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x 页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劄(十二首)
劄(十二首)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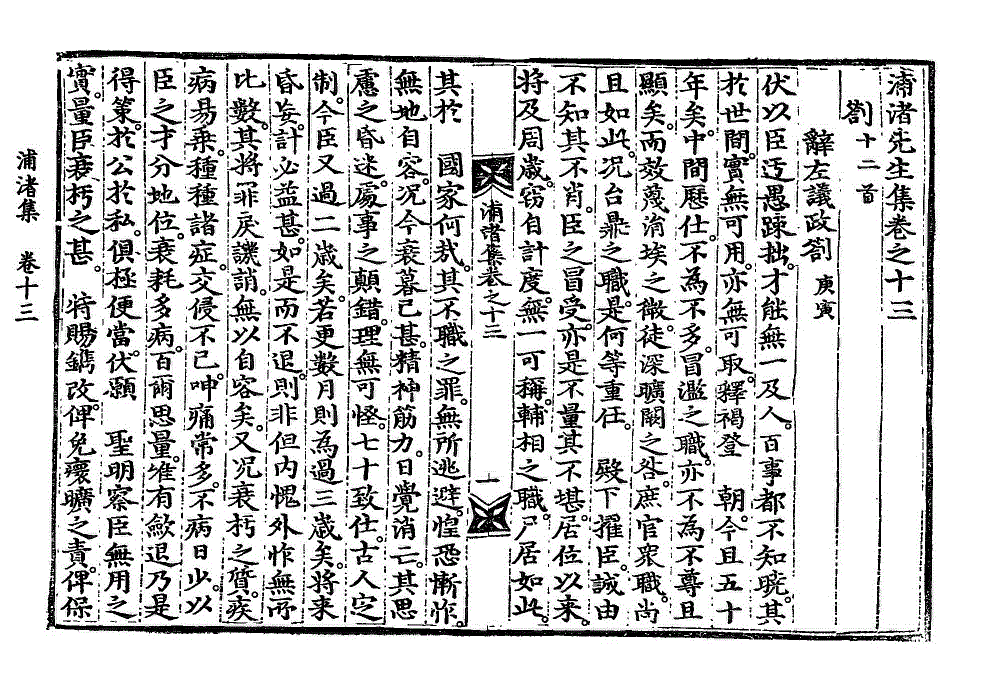 辞左议政劄(庚寅)
辞左议政劄(庚寅)伏以臣迂愚疏拙。才能无一及人。百事都不知晓。其于世间。实无可用。亦无可取。释褐登 朝。今且五十年矣。中间历仕。不为不多。冒滥之职。亦不为不尊且显矣。而效蔑涓埃之微。徒深旷阙之咎。庶官众职。尚且如此。况台鼎之职。是何等重任。 殿下擢臣。诚由不知其不肖。臣之冒受。亦是不量其不堪。居位以来。将及周岁。窃自计度。无一可称。辅相之职。尸居如此。其于 国家何哉。其不职之罪。无所逃避。惶恐惭怍。无地自容。况今衰暮已甚。精神筋力。日觉消亡。其思虑之昏迷。处事之颠错。理无可怪。七十致仕。古人定制。今臣又过二岁矣。若更数月则为过三岁矣。将来昏妄。计必益甚。如是而不退。则非但内愧外怍无所比数。其将罪戾讥诮。无以自容矣。又况衰朽之质。疾病易乘。种种诸症。交侵不已。呻痛常多。不病日少。以臣之才分地位。衰耗多病。百尔思量。唯有敛退乃是得策。于公于私。俱极便当。伏愿 圣明察臣无用之实。量臣衰朽之甚。 特赐镌改。俾免瘝旷之责。俾保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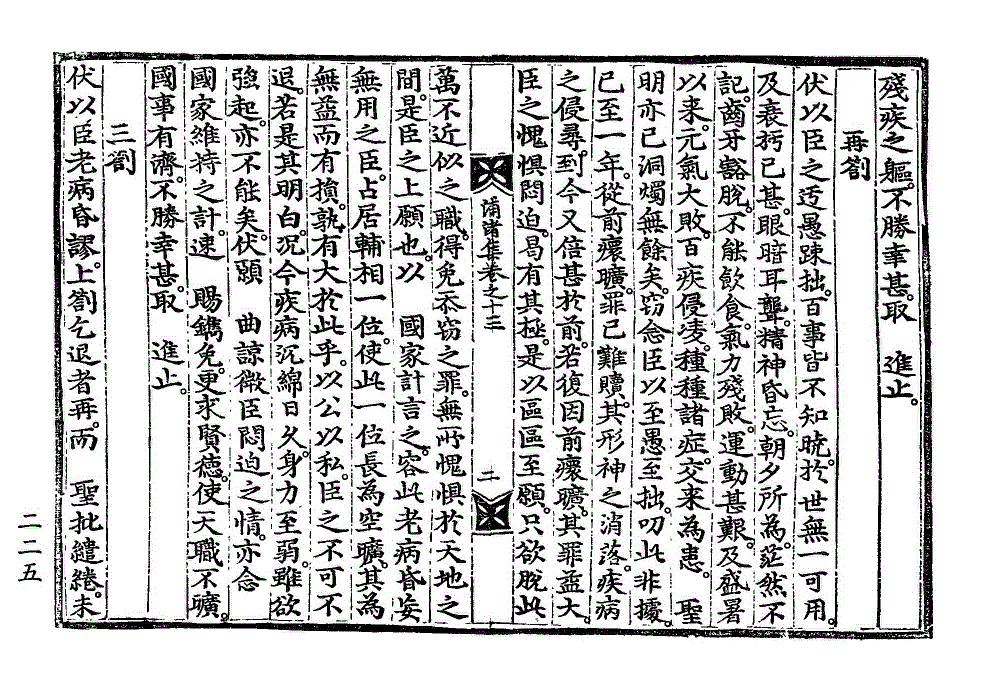 残疾之躯。不胜幸甚。取 进止。
残疾之躯。不胜幸甚。取 进止。辞左议政劄[再劄]
伏以臣之迂愚疏拙。百事皆不知晓。于世无一可用。及衰朽已甚。眼暗耳聋。精神昏忘。朝夕所为。茫然不记。齿牙豁脱。不能饮食。气力残败。运动甚艰。及盛暑以来。元气大败。百疾侵凌。种种诸症。交来为患。 圣明亦已洞烛无馀矣。窃念臣以至愚至拙。叨此非据。已至一年。从前瘝旷。罪已难赎。其形神之消落。疾病之侵寻。到今又倍甚于前。若复因前瘝旷。其罪益大。臣之愧惧闷迫。曷有其极。是以区区至愿。只欲脱此万不近似之职。得免忝窃之罪。无所愧惧于天地之间。是臣之上愿也。以 国家计言之。容此老病昏妄无用之臣。占居辅相一位。使此一位长为空旷。其为无益而有损。孰有大于此乎。以公以私。臣之不可不退。若是其明白。况今疾病沈绵日久。身力至弱。虽欲强起。亦不能矣。伏愿 曲谅微臣闷迫之情。亦念 国家维持之计。速 赐镌免。更求贤德。使天职不旷。国事有济。不胜幸甚。取 进止。
辞左议政劄[三劄]
伏以臣老病昏谬。上劄乞退者再。而 圣批缱绻。未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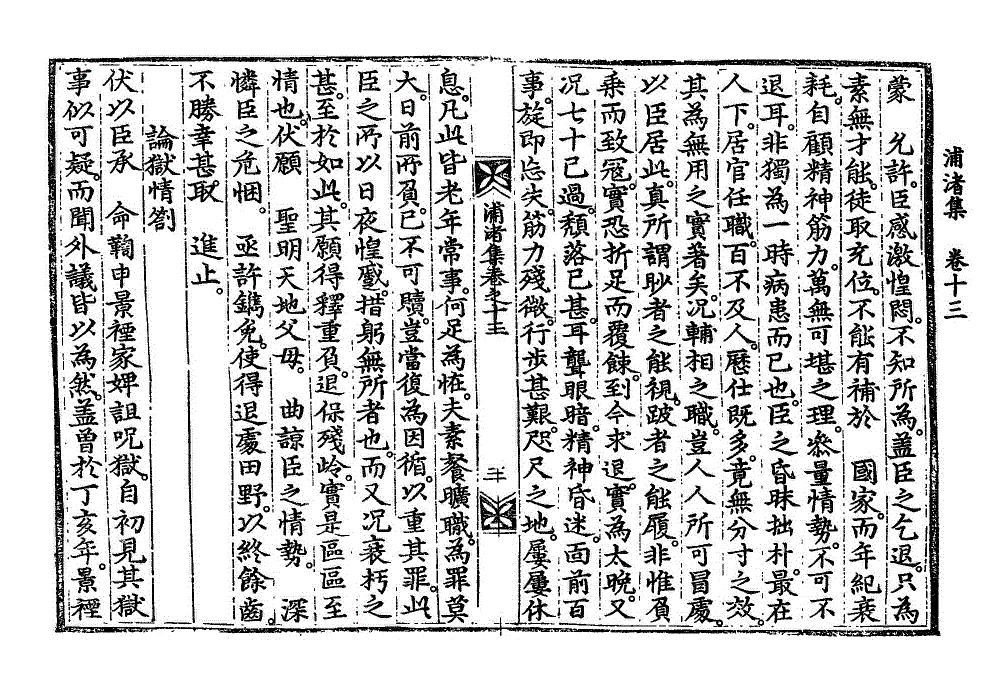 蒙 允许。臣感激惶闷。不知所为。盖臣之乞退。只为素无才能。徒取充位。不能有补于 国家。而年纪衰耗。自顾精神筋力。万无可堪之理。参量情势。不可不退耳。非独为一时病患而已也。臣之昏昧拙朴。最在人下。居官任职。百不及人。历仕既多。竟无分寸之效。其为无用之实著矣。况辅相之职。岂人人所可冒处。以臣居此。真所谓眇者之能视。跛者之能履。非惟负乘而致寇。实恐折足而覆餗。到今求退。实为太晚。又况七十已过。颓落已甚。耳聋眼暗。精神昏迷。面前百事。旋即忘失。筋力残微。行步甚艰。咫尺之地。屡屡休息。凡此皆老年常事。何足为怪。夫素餐旷职。为罪莫大。日前所负。已不可赎。岂当复为因循。以重其罪。此臣之所以日夜惶蹙。措躬无所者也。而又况衰朽之甚。至于如此。其愿得释重负。退保残龄。实是区区至情也。伏愿 圣明天地父母。 曲谅臣之情势。 深怜臣之危悃。 亟许镌免。使得退处田野。以终馀齿。不胜幸甚。取 进止。
蒙 允许。臣感激惶闷。不知所为。盖臣之乞退。只为素无才能。徒取充位。不能有补于 国家。而年纪衰耗。自顾精神筋力。万无可堪之理。参量情势。不可不退耳。非独为一时病患而已也。臣之昏昧拙朴。最在人下。居官任职。百不及人。历仕既多。竟无分寸之效。其为无用之实著矣。况辅相之职。岂人人所可冒处。以臣居此。真所谓眇者之能视。跛者之能履。非惟负乘而致寇。实恐折足而覆餗。到今求退。实为太晚。又况七十已过。颓落已甚。耳聋眼暗。精神昏迷。面前百事。旋即忘失。筋力残微。行步甚艰。咫尺之地。屡屡休息。凡此皆老年常事。何足为怪。夫素餐旷职。为罪莫大。日前所负。已不可赎。岂当复为因循。以重其罪。此臣之所以日夜惶蹙。措躬无所者也。而又况衰朽之甚。至于如此。其愿得释重负。退保残龄。实是区区至情也。伏愿 圣明天地父母。 曲谅臣之情势。 深怜臣之危悃。 亟许镌免。使得退处田野。以终馀齿。不胜幸甚。取 进止。论狱情劄
伏以臣承 命鞫申景禋家婢诅咒狱。自初见其狱事似可疑。而闻外议皆以为然。盖曾于丁亥年。景禋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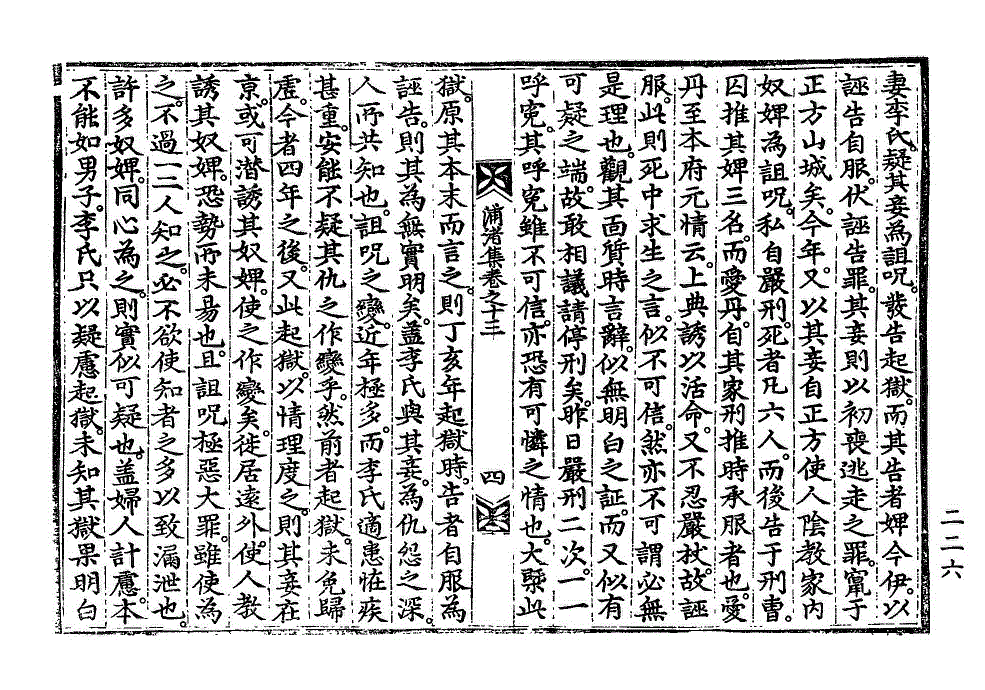 妻李氏。疑其妾为诅咒。发告起狱。而其告者婢今伊。以诬告自服。伏诬告罪。其妾则以初丧逃走之罪。窜于正方山城矣。今年。又以其妾自正方使人阴教家内奴婢为诅咒。私自严刑。死者凡六人。而后告于刑曹。囚推其婢三名。而爱丹。自其家刑推时承服者也。爱丹至本府元情云。上典诱以活命。又不忍严杖。故诬服。此则死中求生之言。似不可信。然亦不可谓必无是理也。观其面质时言辞。似无明白之證。而又似有可疑之端。故敢相议请停刑矣。昨日严刑二次。一一呼冤。其呼冤虽不可信。亦恐有可怜之情也。大概此狱。原其本末而言之。则丁亥年起狱时。告者自服为诬告。则其为无实明矣。盖李氏与其妾。为仇怨之深。人所共知也。诅咒之变。近年极多。而李氏适患怪疾甚重。安能不疑其仇之作变乎。然前者起狱。未免归虚。今者四年之后。又此起狱。以情理度之。则其妾在京。或可潜诱其奴婢。使之作变矣。徙居远外。使人教诱其奴婢。恐势所未易也。且诅咒极恶大罪。虽使为之。不过一二人知之。必不欲使知者之多以致漏泄也。许多奴婢。同心为之。则实似可疑也。盖妇人计虑。本不能如男子。李氏只以疑虑起狱。未知其狱果明白
妻李氏。疑其妾为诅咒。发告起狱。而其告者婢今伊。以诬告自服。伏诬告罪。其妾则以初丧逃走之罪。窜于正方山城矣。今年。又以其妾自正方使人阴教家内奴婢为诅咒。私自严刑。死者凡六人。而后告于刑曹。囚推其婢三名。而爱丹。自其家刑推时承服者也。爱丹至本府元情云。上典诱以活命。又不忍严杖。故诬服。此则死中求生之言。似不可信。然亦不可谓必无是理也。观其面质时言辞。似无明白之證。而又似有可疑之端。故敢相议请停刑矣。昨日严刑二次。一一呼冤。其呼冤虽不可信。亦恐有可怜之情也。大概此狱。原其本末而言之。则丁亥年起狱时。告者自服为诬告。则其为无实明矣。盖李氏与其妾。为仇怨之深。人所共知也。诅咒之变。近年极多。而李氏适患怪疾甚重。安能不疑其仇之作变乎。然前者起狱。未免归虚。今者四年之后。又此起狱。以情理度之。则其妾在京。或可潜诱其奴婢。使之作变矣。徙居远外。使人教诱其奴婢。恐势所未易也。且诅咒极恶大罪。虽使为之。不过一二人知之。必不欲使知者之多以致漏泄也。许多奴婢。同心为之。则实似可疑也。盖妇人计虑。本不能如男子。李氏只以疑虑起狱。未知其狱果明白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27H 页
 无疑。而前后所杀。至十馀人。恐此十馀人未必皆同谋。而今又鞫问此婢。其势必至于死也。人命至重。一人以非罪死。犹极可惜。况此十馀人。未知果皆有当死之罪也。李氏当初诅咒现露。则当取其所得秽物。并其可疑奴婢。呈于刑曹。自官鞫问得实。可也。乃私门杖杀如是之多。其中冤死者亦必有之。此李氏处事。未必十分当理处也。 国家何乃曲从其意乎。故臣之愚意。窃恐此婢不必并杀之也。参鞫诸臣之意亦皆然也。书曰。罪疑惟轻。此正是疑狱也。恐当用惟轻之典也。臣见其疑如此。而一向加刑。所不可忍。故敢此冒陈愚见。伏愿 圣明深察其前后曲折。而有以裁处之。不胜幸甚。取 进止。
无疑。而前后所杀。至十馀人。恐此十馀人未必皆同谋。而今又鞫问此婢。其势必至于死也。人命至重。一人以非罪死。犹极可惜。况此十馀人。未知果皆有当死之罪也。李氏当初诅咒现露。则当取其所得秽物。并其可疑奴婢。呈于刑曹。自官鞫问得实。可也。乃私门杖杀如是之多。其中冤死者亦必有之。此李氏处事。未必十分当理处也。 国家何乃曲从其意乎。故臣之愚意。窃恐此婢不必并杀之也。参鞫诸臣之意亦皆然也。书曰。罪疑惟轻。此正是疑狱也。恐当用惟轻之典也。臣见其疑如此。而一向加刑。所不可忍。故敢此冒陈愚见。伏愿 圣明深察其前后曲折。而有以裁处之。不胜幸甚。取 进止。论 小祥服制劄
伏以臣谨按家礼小祥条陈练服注。男子以练服为冠。去首绖,负版,辟领。丘浚仪节曰。考之韵书。练。沤熟丝也。服问云。三年之丧既练。则服其功衰。杂记。有父母之丧尚功衰注。谓三年丧练后之衰。升数与大功同。故云功衰也。则小祥别有衰。明矣。今拟冠用稍熟麻布为之。服一如大功衰服。而布用稍粗熟麻布为之。温公书仪。谓今人无受服。练服盖不别有所制。惟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27L 页
 仍其旧而已。古礼以小祥为练。小祥而不制练服。可乎。以此所论观之。则小祥之服。当熟布为衰服也。臣曾见此。以为此真得古制也。近者反覆考阅。乃疑其未然也。盖以此所引服问,杂记功衰之文观之。则小祥别有衰。明矣。然其注。只云升数与大功同。而不云其布练熟。以此观之。则窃恐练后之衰。其升数比练前为细。而布则仍用生布不练也。又考檀弓练衣黄里縓缘疏曰。小祥而着练冠。练中衣。故曰练也。练衣者。以练为中衣也。黄里者。黄为中衣也。正服不可变。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縓。浅绛色也。正服。谓衰服也。以此观之。则小祥只练冠与中衣。不练衰服。明矣。然则仪节所谓小祥别有衰。是矣。以熟布为衰。则窃恐其不然也。臣窃见五礼仪。小祥之服只用练冠衰服。则不变 先王朝誊录。皆用此制。此盖从家礼小祥条而然也。今公私大小礼制。皆从家礼。家礼之文既如是。则依此行之固宜也。然礼有节文。古人制礼。自有义意。记曰。丧事有进而无退。故为易以轻服。以间传之文观之。斩衰布。初三升。既虞卒哭。则受以成布六升。以服问,杂记观之。则小祥布升数与大功同。大功服。降服七升。正服八升。是小祥则七升也。大祥
仍其旧而已。古礼以小祥为练。小祥而不制练服。可乎。以此所论观之。则小祥之服。当熟布为衰服也。臣曾见此。以为此真得古制也。近者反覆考阅。乃疑其未然也。盖以此所引服问,杂记功衰之文观之。则小祥别有衰。明矣。然其注。只云升数与大功同。而不云其布练熟。以此观之。则窃恐练后之衰。其升数比练前为细。而布则仍用生布不练也。又考檀弓练衣黄里縓缘疏曰。小祥而着练冠。练中衣。故曰练也。练衣者。以练为中衣也。黄里者。黄为中衣也。正服不可变。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縓。浅绛色也。正服。谓衰服也。以此观之。则小祥只练冠与中衣。不练衰服。明矣。然则仪节所谓小祥别有衰。是矣。以熟布为衰。则窃恐其不然也。臣窃见五礼仪。小祥之服只用练冠衰服。则不变 先王朝誊录。皆用此制。此盖从家礼小祥条而然也。今公私大小礼制。皆从家礼。家礼之文既如是。则依此行之固宜也。然礼有节文。古人制礼。自有义意。记曰。丧事有进而无退。故为易以轻服。以间传之文观之。斩衰布。初三升。既虞卒哭。则受以成布六升。以服问,杂记观之。则小祥布升数与大功同。大功服。降服七升。正服八升。是小祥则七升也。大祥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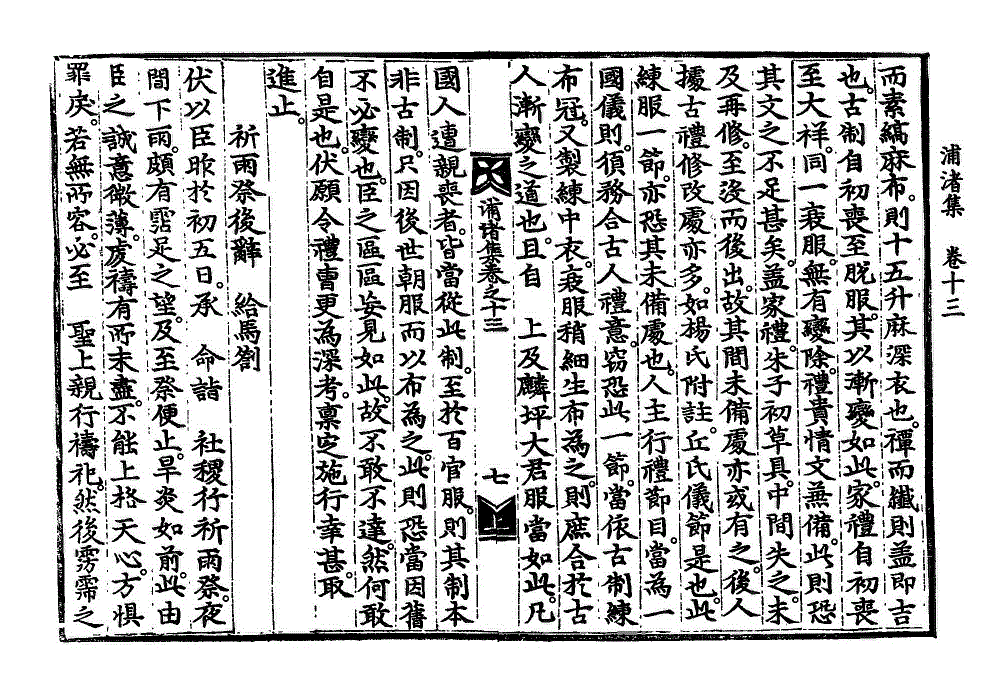 而素缟麻布。则十五升麻深衣也。禫而纤则盖即吉也。古制自初丧至脱服。其以渐变如此。家礼自初丧至大祥。同一衰服。无有变除。礼贵情文兼备。此则恐其文之不足甚矣。盖家礼。朱子初草具。中间失之。未及再修。至没而后出。故其间未备处亦或有之。后人据古礼修改处亦多。如杨氏附注。丘氏仪节是也。此练服一节。亦恐其未备处也。人主行礼节目。当为一国仪则。须务合古人礼意。窃恐此一节。当依古制练布冠。又制练中衣。衰服稍细生布为之。则庶合于古人渐变之道也。且自 上及麟坪大君服当如此。凡国人遭亲丧者。皆当从此制。至于百官服。则其制本非古制。只因后世朝服而以布为之。此则恐当因旧不必变也。臣之区区妄见如此。故不敢不达。然何敢自是也。伏愿令礼曹更为深考。禀定施行幸甚。取 进止。
而素缟麻布。则十五升麻深衣也。禫而纤则盖即吉也。古制自初丧至脱服。其以渐变如此。家礼自初丧至大祥。同一衰服。无有变除。礼贵情文兼备。此则恐其文之不足甚矣。盖家礼。朱子初草具。中间失之。未及再修。至没而后出。故其间未备处亦或有之。后人据古礼修改处亦多。如杨氏附注。丘氏仪节是也。此练服一节。亦恐其未备处也。人主行礼节目。当为一国仪则。须务合古人礼意。窃恐此一节。当依古制练布冠。又制练中衣。衰服稍细生布为之。则庶合于古人渐变之道也。且自 上及麟坪大君服当如此。凡国人遭亲丧者。皆当从此制。至于百官服。则其制本非古制。只因后世朝服而以布为之。此则恐当因旧不必变也。臣之区区妄见如此。故不敢不达。然何敢自是也。伏愿令礼曹更为深考。禀定施行幸甚。取 进止。祈雨祭后辞 给马劄
伏以臣昨于初五日。承 命诣 社稷行祈雨祭。夜间下雨。颇有沾足之望。及至祭便止。旱炎如前。此由臣之诚意微薄。虔祷有所未尽。不能上格天心。方惧罪戾。若无所容。必至 圣上亲行祷祀。然后霶霈之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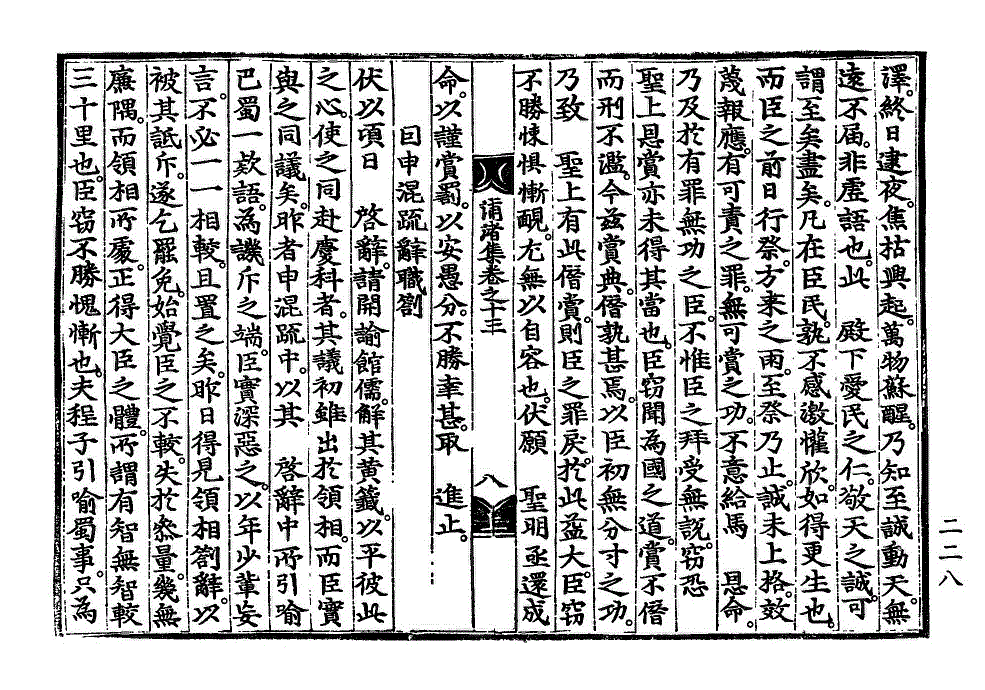 泽。终日逮夜。焦枯兴起。万物苏醒。乃知至诚动天。无远不届。非虚语也。此 殿下爱民之仁。敬天之诚。可谓至矣尽矣。凡在臣民。孰不感激欢欣。如得更生也。而臣之前日行祭。方来之雨。至祭乃止。诚未上格。效蔑报应。有可责之罪。无可赏之功。不意给马 恩命。乃及于有罪无功之臣。不惟臣之拜受无说。窃恐 圣上恩赏亦未得其当也。臣窃闻为国之道。赏不僭而刑不滥。今兹赏典。僭孰甚焉。以臣初无分寸之功。乃致 圣上有此僭赏。则臣之罪戾。于此益大。臣窃不胜悚惧惭腼。尤无以自容也。伏愿 圣明亟还成命。以谨赏罚。以安愚分。不胜幸甚。取 进止。
泽。终日逮夜。焦枯兴起。万物苏醒。乃知至诚动天。无远不届。非虚语也。此 殿下爱民之仁。敬天之诚。可谓至矣尽矣。凡在臣民。孰不感激欢欣。如得更生也。而臣之前日行祭。方来之雨。至祭乃止。诚未上格。效蔑报应。有可责之罪。无可赏之功。不意给马 恩命。乃及于有罪无功之臣。不惟臣之拜受无说。窃恐 圣上恩赏亦未得其当也。臣窃闻为国之道。赏不僭而刑不滥。今兹赏典。僭孰甚焉。以臣初无分寸之功。乃致 圣上有此僭赏。则臣之罪戾。于此益大。臣窃不胜悚惧惭腼。尤无以自容也。伏愿 圣明亟还成命。以谨赏罚。以安愚分。不胜幸甚。取 进止。因申混疏辞职劄
伏以顷日 启辞。请开谕馆儒。解其黄签。以平彼此之心。使之同赴庆科者。其议初虽出于领相。而臣实与之同议矣。昨者申混疏中。以其 启辞中所引喻巴蜀一款语。为讥斥之端。臣实深恶之。以年少辈妄言。不必一一相较。且置之矣。昨日得见领相劄辞。以被其诋斥。遂乞罢免。始觉臣之不较。失于参量。几无廉隅。而领相所处。正得大臣之体。所谓有智无智较三十里也。臣窃不胜愧惭也。夫程子引喻蜀事。只为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29H 页
 叹当时风俗之失。子弟不从父兄之命言。古者子弟从父兄。引汉高下沛时谕沛父老。及相如使蜀。通道西南夷。谕蜀父老事以证之。蜀自秦惠王时已属于秦。至汉武帝时。其为中国地已久矣。相如亦蜀人也。谓之梗化之地者。乃虚语也。臣等之 启。引此事者。只欲谕岭南士子之父兄。使教其子弟赴试也。待以梗化。则臣等实无毫发此意也。申混欲咎臣等。乃以蜀为梗化之地。是设非实之言。怒岭儒之心。摭无情之语。诋臣等之失。不亦妄乎。领相既以辞退。臣何颜独冒居乎。伏愿 圣明量察臣之事体情势。亟 赐镌免。以安愚分。不胜幸甚。且审察其疏辞。多有可怪之语。引王凤专威福事。比之于今日。臣以至庸极陋。待罪相位。其引王凤事者。乃指相臣也。以此思之。不觉心骨悚慄也。 殿下见臣等有一毫专擅之事乎。臣本轻浅疏拙。素不为人所畏惮。又不善交人。游从绝少。忝冒日久。一事不得行。而门庭寂然。绝无朝士来见者。或有来见者。只是故旧相访。要路当事之人。其迹绝疏。宰相无权无威。岂有如臣者乎。如是而尚冒居。实可耻之甚也。混乃比之于王凤。何其比拟非伦若是也。此尤臣之所以不可一日安于朝廷者也。
叹当时风俗之失。子弟不从父兄之命言。古者子弟从父兄。引汉高下沛时谕沛父老。及相如使蜀。通道西南夷。谕蜀父老事以证之。蜀自秦惠王时已属于秦。至汉武帝时。其为中国地已久矣。相如亦蜀人也。谓之梗化之地者。乃虚语也。臣等之 启。引此事者。只欲谕岭南士子之父兄。使教其子弟赴试也。待以梗化。则臣等实无毫发此意也。申混欲咎臣等。乃以蜀为梗化之地。是设非实之言。怒岭儒之心。摭无情之语。诋臣等之失。不亦妄乎。领相既以辞退。臣何颜独冒居乎。伏愿 圣明量察臣之事体情势。亟 赐镌免。以安愚分。不胜幸甚。且审察其疏辞。多有可怪之语。引王凤专威福事。比之于今日。臣以至庸极陋。待罪相位。其引王凤事者。乃指相臣也。以此思之。不觉心骨悚慄也。 殿下见臣等有一毫专擅之事乎。臣本轻浅疏拙。素不为人所畏惮。又不善交人。游从绝少。忝冒日久。一事不得行。而门庭寂然。绝无朝士来见者。或有来见者。只是故旧相访。要路当事之人。其迹绝疏。宰相无权无威。岂有如臣者乎。如是而尚冒居。实可耻之甚也。混乃比之于王凤。何其比拟非伦若是也。此尤臣之所以不可一日安于朝廷者也。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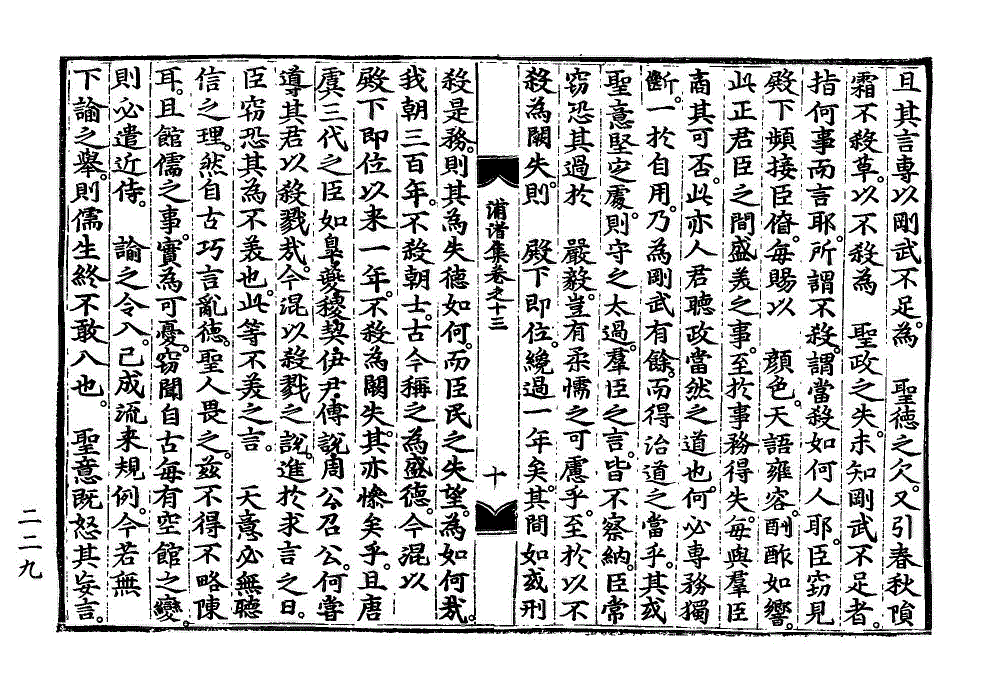 且其言专以刚武不足。为 圣德之欠。又引春秋陨霜不杀草。以不杀为 圣政之失。未知刚武不足者。指何事而言耶。所谓不杀。谓当杀如何人耶。臣窃见殿下频接臣僚。每赐以 颜色。天语雍容。酬酢如响。此正君臣之间盛美之事。至于事务得失。每与群臣商其可否。此亦人君听政当然之道也。何必专务独断。一于自用。乃为刚武有馀。而得治道之当乎。其或圣意坚定处。则守之太过。群臣之言。皆不察纳。臣常窃恐其过于 严毅。岂有柔懦之可虑乎。至于以不杀为阙失。则 殿下即位。才过一年矣。其间如或刑杀是务。则其为失德如何。而臣民之失望。为如何哉。我朝三百年。不杀朝士。古今称之为盛德。今混以 殿下即位以来一年。不杀为阙失。其亦惨矣乎。且唐虞三代之臣如皋,夔,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何尝导其君以杀戮哉。今混以杀戮之说。进于求言之日。臣窃恐其为不美也。此等不美之言。 天意必无听信之理。然自古巧言乱德。圣人畏之。兹不得不略陈耳。且馆儒之事。实为可忧。窃闻自古每有空馆之变。则必遣近侍。 谕之令入。已成流来规例。今若无 下谕之举。则儒生终不敢入也。 圣意既怒其妄言。
且其言专以刚武不足。为 圣德之欠。又引春秋陨霜不杀草。以不杀为 圣政之失。未知刚武不足者。指何事而言耶。所谓不杀。谓当杀如何人耶。臣窃见殿下频接臣僚。每赐以 颜色。天语雍容。酬酢如响。此正君臣之间盛美之事。至于事务得失。每与群臣商其可否。此亦人君听政当然之道也。何必专务独断。一于自用。乃为刚武有馀。而得治道之当乎。其或圣意坚定处。则守之太过。群臣之言。皆不察纳。臣常窃恐其过于 严毅。岂有柔懦之可虑乎。至于以不杀为阙失。则 殿下即位。才过一年矣。其间如或刑杀是务。则其为失德如何。而臣民之失望。为如何哉。我朝三百年。不杀朝士。古今称之为盛德。今混以 殿下即位以来一年。不杀为阙失。其亦惨矣乎。且唐虞三代之臣如皋,夔,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何尝导其君以杀戮哉。今混以杀戮之说。进于求言之日。臣窃恐其为不美也。此等不美之言。 天意必无听信之理。然自古巧言乱德。圣人畏之。兹不得不略陈耳。且馆儒之事。实为可忧。窃闻自古每有空馆之变。则必遣近侍。 谕之令入。已成流来规例。今若无 下谕之举。则儒生终不敢入也。 圣意既怒其妄言。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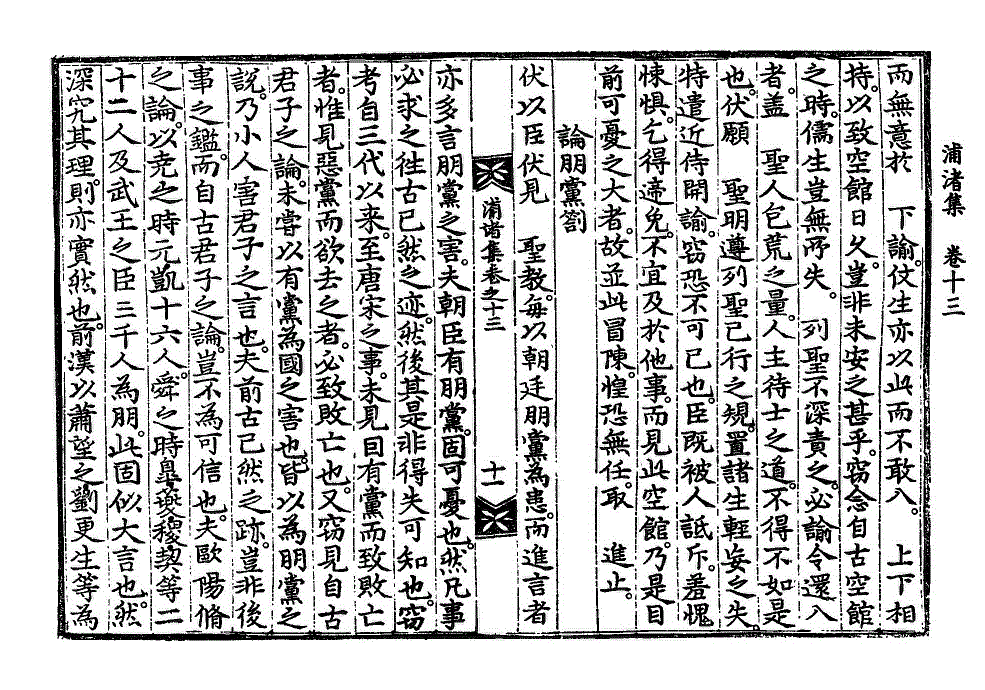 而无意于 下谕。儒生亦以此而不敢入。 上下相持。以致空馆日久。岂非未安之甚乎。窃念自古空馆之时。儒生岂无所失。 列圣不深责之。必谕令还入者。盖 圣人包荒之量。人主待士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伏愿 圣明遵列圣已行之规。置诸生轻妄之失。特遣近侍开谕。窃恐不可已也。臣既被人诋斥。羞愧悚惧。乞得递免。不宜及于他事。而见此空馆。乃是目前可忧之大者。故并此冒陈。惶恐无任。取 进止。
而无意于 下谕。儒生亦以此而不敢入。 上下相持。以致空馆日久。岂非未安之甚乎。窃念自古空馆之时。儒生岂无所失。 列圣不深责之。必谕令还入者。盖 圣人包荒之量。人主待士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伏愿 圣明遵列圣已行之规。置诸生轻妄之失。特遣近侍开谕。窃恐不可已也。臣既被人诋斥。羞愧悚惧。乞得递免。不宜及于他事。而见此空馆。乃是目前可忧之大者。故并此冒陈。惶恐无任。取 进止。论朋党劄
伏以臣伏见 圣教。每以朝廷朋党为患。而进言者亦多言朋党之害。夫朝臣有朋党。固可忧也。然凡事必求之往古已然之迹。然后其是非得失可知也。窃考自三代以来。至唐宋之事。未见因有党而致败亡者。惟见恶党而欲去之者。必致败亡也。又窃见自古君子之论。未尝以有党为国之害也。皆以为朋党之说。乃小人害君子之言也。夫前古已然之迹。岂非后事之鉴。而自古君子之论。岂不为可信也。夫欧阳脩之论。以尧之时元,凯十六人。舜之时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及武王之臣三千人为朋。此固似大言也。然深究其理。则亦实然也。前汉以萧望之,刘更生等为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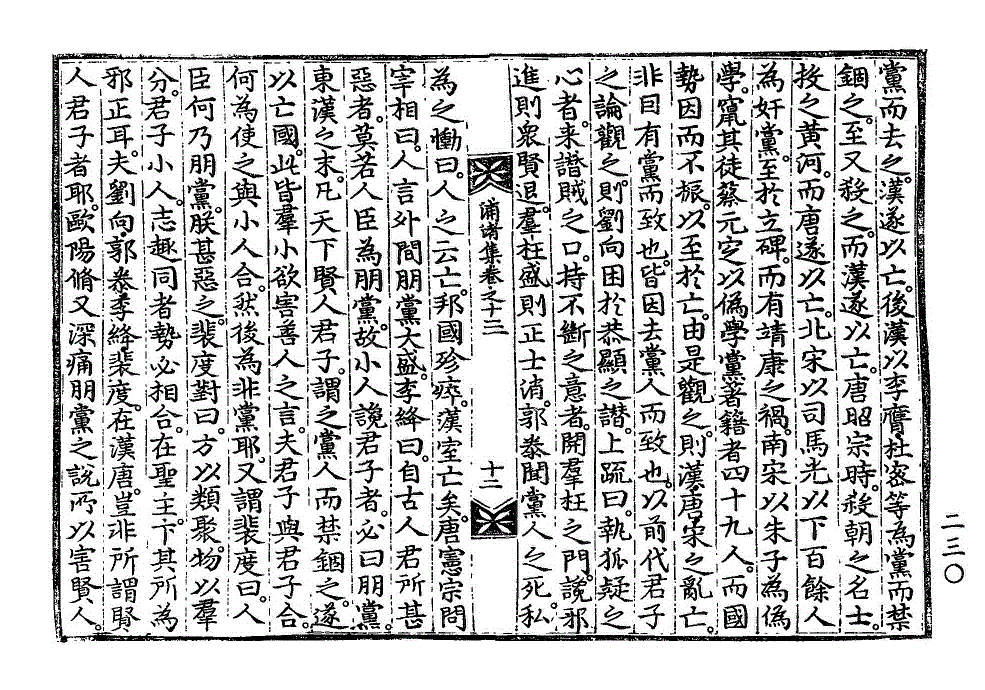 党而去之。汉遂以亡。后汉以李膺,杜密等为党而禁锢之。至又杀之。而汉遂以亡。唐昭宗时。杀朝之名士。投之黄河。而唐遂以亡。北宋以司马光以下百馀人为奸党。至于立碑。而有靖康之祸。南宋以朱子为伪学。窜其徒蔡元定以伪学党著籍者四十九人。而国势因而不振。以至于亡。由是观之。则汉,唐,宋之乱亡。非因有党而致也。皆因去党人而致也。以前代君子之论观之。则刘向困于恭显之谮。上疏曰。执狐疑之心者。来谮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郭泰闻党人之死。私为之恸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亡矣。唐宪宗问宰相曰。人言外间朋党大盛。李绛曰。自古人君所甚恶者。莫若人臣为朋党。故小人谗君子者。必曰朋党。东汉之末。凡天下贤人君子。谓之党人而禁锢之。遂以亡国。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夫君子与君子合。何为使之与小人合。然后为非党耶。又谓裴度曰。人臣何乃朋党。朕甚恶之。裴度对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势必相合。在圣主。卞其所为邪正耳。夫刘向,郭泰,李绛,裴度。在汉唐。岂非所谓贤人君子者耶。欧阳脩又深痛朋党之说所以害贤人。
党而去之。汉遂以亡。后汉以李膺,杜密等为党而禁锢之。至又杀之。而汉遂以亡。唐昭宗时。杀朝之名士。投之黄河。而唐遂以亡。北宋以司马光以下百馀人为奸党。至于立碑。而有靖康之祸。南宋以朱子为伪学。窜其徒蔡元定以伪学党著籍者四十九人。而国势因而不振。以至于亡。由是观之。则汉,唐,宋之乱亡。非因有党而致也。皆因去党人而致也。以前代君子之论观之。则刘向困于恭显之谮。上疏曰。执狐疑之心者。来谮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郭泰闻党人之死。私为之恸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亡矣。唐宪宗问宰相曰。人言外间朋党大盛。李绛曰。自古人君所甚恶者。莫若人臣为朋党。故小人谗君子者。必曰朋党。东汉之末。凡天下贤人君子。谓之党人而禁锢之。遂以亡国。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夫君子与君子合。何为使之与小人合。然后为非党耶。又谓裴度曰。人臣何乃朋党。朕甚恶之。裴度对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势必相合。在圣主。卞其所为邪正耳。夫刘向,郭泰,李绛,裴度。在汉唐。岂非所谓贤人君子者耶。欧阳脩又深痛朋党之说所以害贤人。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31H 页
 其在谏院。著朋党论以进。又于唐书论之曰。当汉之亡也。先以朋党。禁锢天下贤人君子。而立朝者皆小人也。然后汉从以亡。唐之亡也。又以朋党。尽杀朝廷之士。而馀存者皆庸懦不肖倾险之人也。然后唐从以亡。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与人者。必进朋党之说。其言尤痛切。朱子与留相书曰。朋党之祸出于搢绅。而古之恶朋党而欲去之者。往往至于亡人之国。盖不察其贤否忠邪。而惟党之务去。则彼小人之巧于自谋者。必将有以自盖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无所回互。往往反为所挤。而目以为党。汉唐绍圣之已事。今未远也。又曰。愿丞相先以分别贤否忠邪为己任。其果贤且忠耶。则显然进之。犹恐其党之不多而无与共图天下之事也。其果奸且邪耶。则显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尽有以害吾用贤之功也。不惟不惮以身为之党。又将引吾君以为党而不惮也。以此观之。则自古贤人君子。皆不恶有党。而惟恶其告人为党者也。盖人臣有私党。人主必恶之者。乃恐其相率而为欺负也。然只观其人贤否而已。若贤也。则当诚心事君。其朋虽多。岂有
其在谏院。著朋党论以进。又于唐书论之曰。当汉之亡也。先以朋党。禁锢天下贤人君子。而立朝者皆小人也。然后汉从以亡。唐之亡也。又以朋党。尽杀朝廷之士。而馀存者皆庸懦不肖倾险之人也。然后唐从以亡。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与人者。必进朋党之说。其言尤痛切。朱子与留相书曰。朋党之祸出于搢绅。而古之恶朋党而欲去之者。往往至于亡人之国。盖不察其贤否忠邪。而惟党之务去。则彼小人之巧于自谋者。必将有以自盖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无所回互。往往反为所挤。而目以为党。汉唐绍圣之已事。今未远也。又曰。愿丞相先以分别贤否忠邪为己任。其果贤且忠耶。则显然进之。犹恐其党之不多而无与共图天下之事也。其果奸且邪耶。则显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尽有以害吾用贤之功也。不惟不惮以身为之党。又将引吾君以为党而不惮也。以此观之。则自古贤人君子。皆不恶有党。而惟恶其告人为党者也。盖人臣有私党。人主必恶之者。乃恐其相率而为欺负也。然只观其人贤否而已。若贤也。则当诚心事君。其朋虽多。岂有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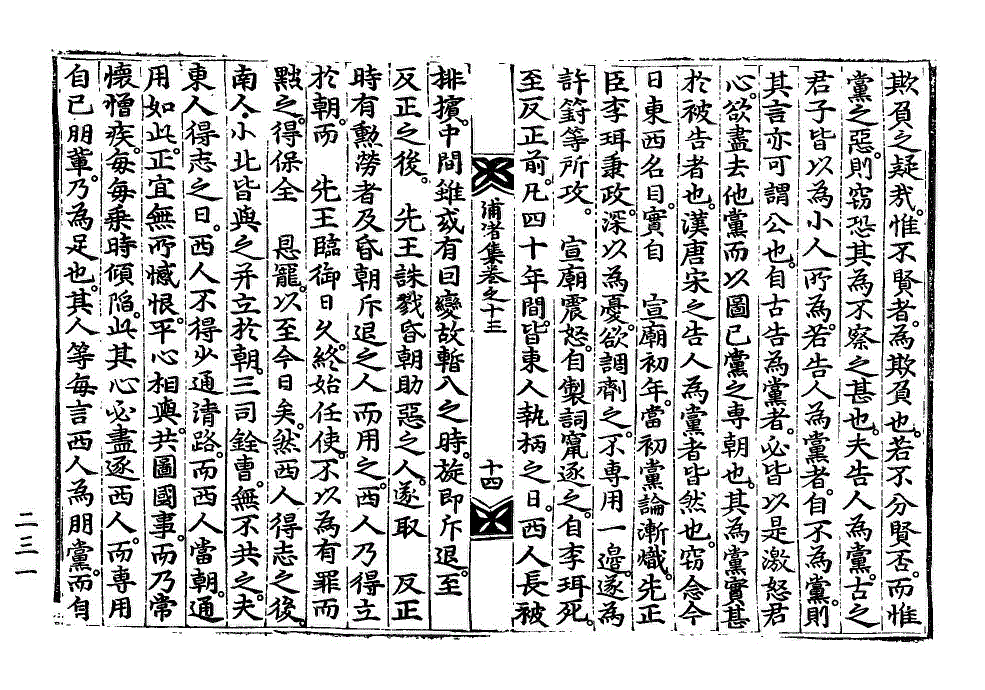 欺负之疑哉。惟不贤者。为欺负也。若不分贤否。而惟党之恶。则窃恐其为不察之甚也。夫告人为党。古之君子皆以为小人所为。若告人为党者。自不为党。则其言亦可谓公也。自古告为党者。必皆以是激怒君心。欲尽去他党而以图己党之专朝也。其为党实甚于被告者也。汉唐宋之告人为党者皆然也。窃念今日东西名目。实自 宣庙初年。当初党论渐炽。先正臣李珥秉政。深以为忧。欲调剂之。不专用一边。遂为许篈等所攻。 宣庙震怒。自制词窜逐之。自李珥死。至反正前。凡四十年间。皆东人执柄之日。西人长被排摈。中间虽或有因变故暂入之时。旋即斥退。至 反正之后。 先王诛戮昏朝助恶之人。遂取 反正时有勋劳者及昏朝斥退之人而用之。西人乃得立于朝。而 先王临御日久。终始任使。不以为有罪而黜之。得保全 恩宠。以至今日矣。然西人得志之后。南人,小北皆与之并立于朝。三司铨曹。无不共之。夫东人得志之日。西人不得少通清路。而西人当朝。通用如此。正宜无所憾恨。平心相与。共图国事。而乃常怀憎疾。每每乘时倾陷。此其心必尽逐西人。而专用自己朋辈。乃为足也。其人等每言西人为朋党。而自
欺负之疑哉。惟不贤者。为欺负也。若不分贤否。而惟党之恶。则窃恐其为不察之甚也。夫告人为党。古之君子皆以为小人所为。若告人为党者。自不为党。则其言亦可谓公也。自古告为党者。必皆以是激怒君心。欲尽去他党而以图己党之专朝也。其为党实甚于被告者也。汉唐宋之告人为党者皆然也。窃念今日东西名目。实自 宣庙初年。当初党论渐炽。先正臣李珥秉政。深以为忧。欲调剂之。不专用一边。遂为许篈等所攻。 宣庙震怒。自制词窜逐之。自李珥死。至反正前。凡四十年间。皆东人执柄之日。西人长被排摈。中间虽或有因变故暂入之时。旋即斥退。至 反正之后。 先王诛戮昏朝助恶之人。遂取 反正时有勋劳者及昏朝斥退之人而用之。西人乃得立于朝。而 先王临御日久。终始任使。不以为有罪而黜之。得保全 恩宠。以至今日矣。然西人得志之后。南人,小北皆与之并立于朝。三司铨曹。无不共之。夫东人得志之日。西人不得少通清路。而西人当朝。通用如此。正宜无所憾恨。平心相与。共图国事。而乃常怀憎疾。每每乘时倾陷。此其心必尽逐西人。而专用自己朋辈。乃为足也。其人等每言西人为朋党。而自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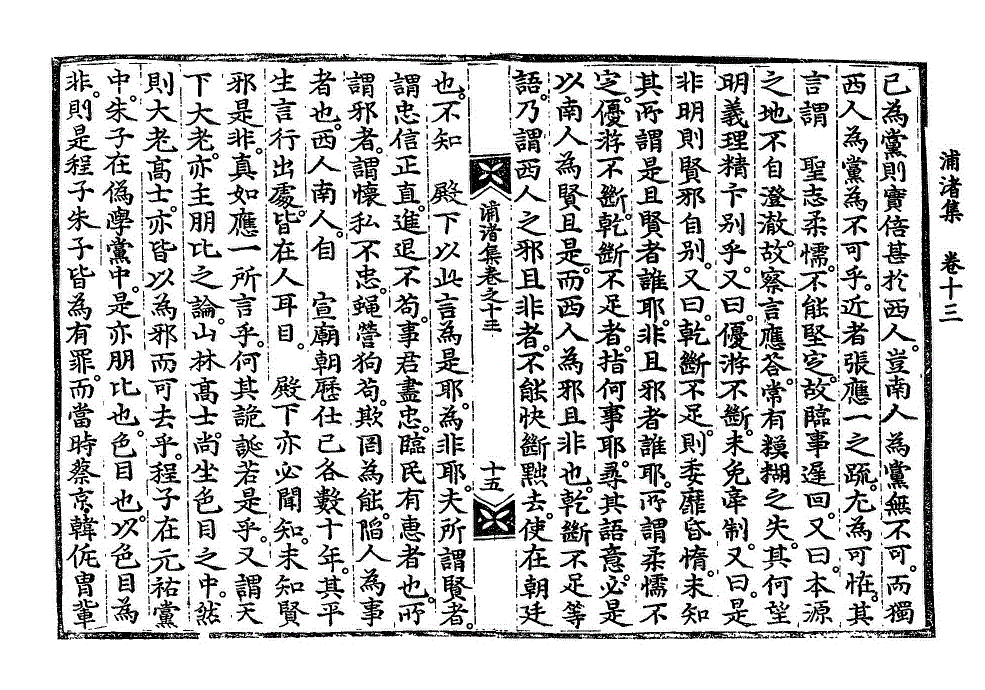 己为党则实倍甚于西人。岂南人为党无不可。而独西人为党为不可乎。近者张应一之疏。尤为可怪。其言谓 圣志柔懦。不能坚定。故临事迟回。又曰。本源之地不自澄澈。故察言应答。常有模糊之失。其何望明义理精卞别乎。又曰。优游不断。未免牵制。又曰。是非明则贤邪自别。又曰。乾断不足。则委靡昏惰。未知其所谓是且贤者谁耶。非且邪者谁耶。所谓柔懦不定。优游不断。乾断不足者。指何事耶。寻其语意。必是以南人为贤且是。而西人为邪且非也。乾断不足等语。乃谓西人之邪且非者。不能快断黜去。使在朝廷也。不知 殿下以此言为是耶。为非耶。夫所谓贤者。谓忠信正直。进退不苟。事君尽忠。临民有惠者也。所谓邪者。谓怀私不忠。蝇营狗苟。欺罔为能。陷人为事者也。西人南人。自 宣庙朝历仕已各数十年。其平生言行出处。皆在人耳目。 殿下亦必闻知。未知贤邪是非。真如应一所言乎。何其诡诞若是乎。又谓天下大老。亦主朋比之论。山林高士。尚坐色目之中。然则大老高士。亦皆以为邪而可去乎。程子在元祐党中。朱子在伪学党中。是亦朋比也。色目也。以色目为非。则是程子朱子皆为有罪。而当时蔡京,韩侂胄辈
己为党则实倍甚于西人。岂南人为党无不可。而独西人为党为不可乎。近者张应一之疏。尤为可怪。其言谓 圣志柔懦。不能坚定。故临事迟回。又曰。本源之地不自澄澈。故察言应答。常有模糊之失。其何望明义理精卞别乎。又曰。优游不断。未免牵制。又曰。是非明则贤邪自别。又曰。乾断不足。则委靡昏惰。未知其所谓是且贤者谁耶。非且邪者谁耶。所谓柔懦不定。优游不断。乾断不足者。指何事耶。寻其语意。必是以南人为贤且是。而西人为邪且非也。乾断不足等语。乃谓西人之邪且非者。不能快断黜去。使在朝廷也。不知 殿下以此言为是耶。为非耶。夫所谓贤者。谓忠信正直。进退不苟。事君尽忠。临民有惠者也。所谓邪者。谓怀私不忠。蝇营狗苟。欺罔为能。陷人为事者也。西人南人。自 宣庙朝历仕已各数十年。其平生言行出处。皆在人耳目。 殿下亦必闻知。未知贤邪是非。真如应一所言乎。何其诡诞若是乎。又谓天下大老。亦主朋比之论。山林高士。尚坐色目之中。然则大老高士。亦皆以为邪而可去乎。程子在元祐党中。朱子在伪学党中。是亦朋比也。色目也。以色目为非。则是程子朱子皆为有罪。而当时蔡京,韩侂胄辈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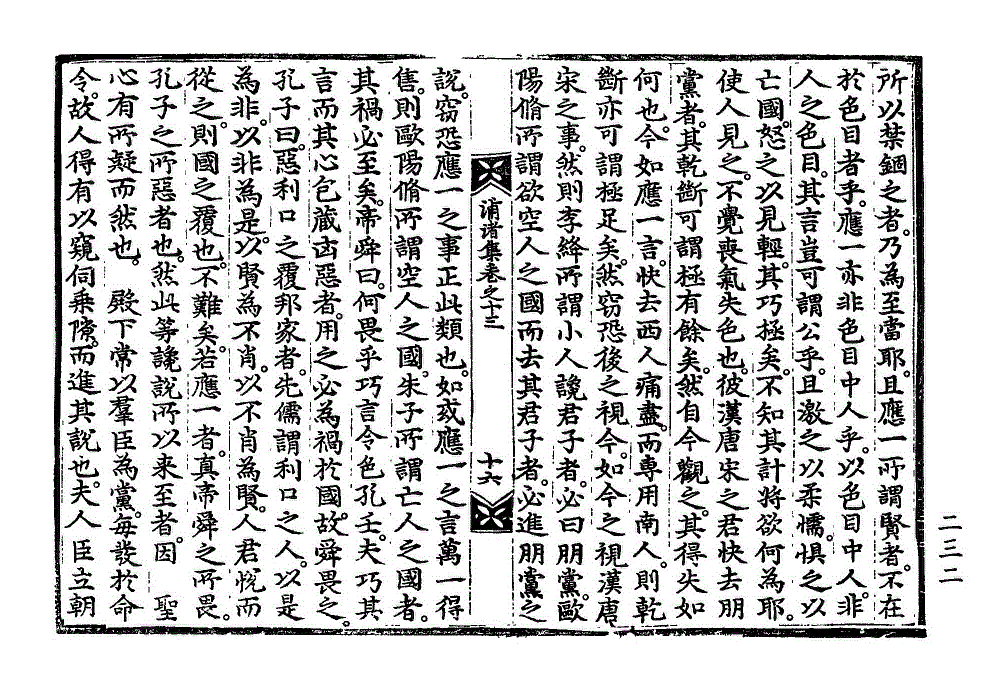 所以禁锢之者。乃为至当耶。且应一所谓贤者。不在于色目者乎。应一亦非色目中人乎。以色目中人。非人之色目。其言岂可谓公乎。且激之以柔懦。惧之以亡国。怒之以见轻。其巧极矣。不知其计将欲何为耶。使人见之。不觉丧气失色也。彼汉唐宋之君快去朋党者。其乾断可谓极有馀矣。然自今观之。其得失如何也。今如应一言。快去西人痛尽。而专用南人。则乾断亦可谓极足矣。然窃恐后之视今。如今之视汉唐宋之事。然则李绛所谓小人谗君子者。必曰朋党。欧阳脩所谓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窃恐应一之事正此类也。如或应一之言万一得售。则欧阳脩所谓空人之国。朱子所谓亡人之国者。其祸必至矣。帝舜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夫巧其言而其心包藏凶恶者。用之必为祸于国。故舜畏之。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先儒谓利口之人。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人君悦而从之。则国之覆也。不难矣。若应一者。真帝舜之所畏。孔子之所恶者也。然此等谗说所以来至者。因 圣心有所疑而然也。 殿下常以群臣为党。每发于命令。故人得有以窥伺乘隙。而进其说也。夫人臣立朝
所以禁锢之者。乃为至当耶。且应一所谓贤者。不在于色目者乎。应一亦非色目中人乎。以色目中人。非人之色目。其言岂可谓公乎。且激之以柔懦。惧之以亡国。怒之以见轻。其巧极矣。不知其计将欲何为耶。使人见之。不觉丧气失色也。彼汉唐宋之君快去朋党者。其乾断可谓极有馀矣。然自今观之。其得失如何也。今如应一言。快去西人痛尽。而专用南人。则乾断亦可谓极足矣。然窃恐后之视今。如今之视汉唐宋之事。然则李绛所谓小人谗君子者。必曰朋党。欧阳脩所谓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窃恐应一之事正此类也。如或应一之言万一得售。则欧阳脩所谓空人之国。朱子所谓亡人之国者。其祸必至矣。帝舜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夫巧其言而其心包藏凶恶者。用之必为祸于国。故舜畏之。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先儒谓利口之人。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人君悦而从之。则国之覆也。不难矣。若应一者。真帝舜之所畏。孔子之所恶者也。然此等谗说所以来至者。因 圣心有所疑而然也。 殿下常以群臣为党。每发于命令。故人得有以窥伺乘隙。而进其说也。夫人臣立朝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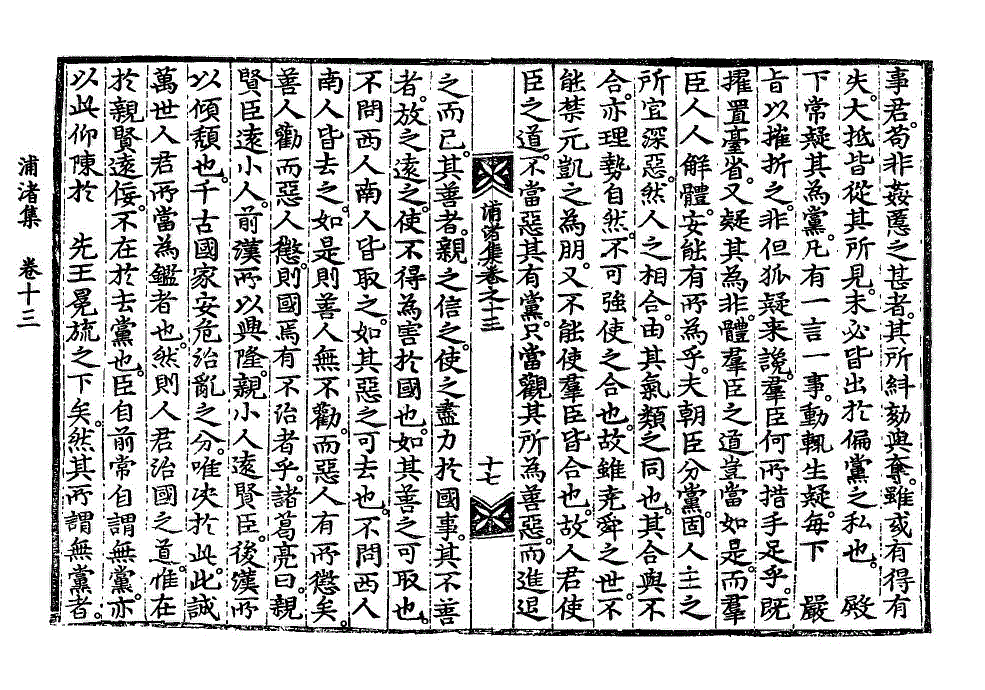 事君。苟非奸慝之甚者。其所纠劾与夺。虽或有得有失。大抵皆从其所见。未必皆出于偏党之私也。 殿下常疑其为党。凡有一言一事。动辄生疑。每下 严旨以摧折之。非但狐疑来谗。群臣何所措手足乎。既擢置台省。又疑其为非。体群臣之道岂当如是。而群臣人人解体。安能有所为乎。夫朝臣分党。固人主之所宜深恶。然人之相合。由其气类之同也。其合与不合。亦理势自然。不可强使之合也。故虽尧舜之世。不能禁元凯之为朋。又不能使群臣皆合也。故人君使臣之道。不当恶其有党。只当观其所为善恶。而进退之而已。其善者。亲之信之。使之尽力于国事。其不善者。放之远之。使不得为害于国也。如其善之可取也。不问西人南人皆取之。如其恶之可去也。不问西人南人皆去之。如是则善人无不劝。而恶人有所惩矣。善人劝而恶人惩。则国焉有不治者乎。诸葛亮曰。亲贤臣远小人。前汉所以兴隆。亲小人远贤臣。后汉所以倾颓也。千古国家安危治乱之分。唯决于此。此诚万世人君所当为鉴者也。然则人君治国之道。惟在于亲贤远佞。不在于去党也。臣自前常自谓无党。亦以此仰陈于 先王冕旒之下矣。然其所谓无党者。
事君。苟非奸慝之甚者。其所纠劾与夺。虽或有得有失。大抵皆从其所见。未必皆出于偏党之私也。 殿下常疑其为党。凡有一言一事。动辄生疑。每下 严旨以摧折之。非但狐疑来谗。群臣何所措手足乎。既擢置台省。又疑其为非。体群臣之道岂当如是。而群臣人人解体。安能有所为乎。夫朝臣分党。固人主之所宜深恶。然人之相合。由其气类之同也。其合与不合。亦理势自然。不可强使之合也。故虽尧舜之世。不能禁元凯之为朋。又不能使群臣皆合也。故人君使臣之道。不当恶其有党。只当观其所为善恶。而进退之而已。其善者。亲之信之。使之尽力于国事。其不善者。放之远之。使不得为害于国也。如其善之可取也。不问西人南人皆取之。如其恶之可去也。不问西人南人皆去之。如是则善人无不劝。而恶人有所惩矣。善人劝而恶人惩。则国焉有不治者乎。诸葛亮曰。亲贤臣远小人。前汉所以兴隆。亲小人远贤臣。后汉所以倾颓也。千古国家安危治乱之分。唯决于此。此诚万世人君所当为鉴者也。然则人君治国之道。惟在于亲贤远佞。不在于去党也。臣自前常自谓无党。亦以此仰陈于 先王冕旒之下矣。然其所谓无党者。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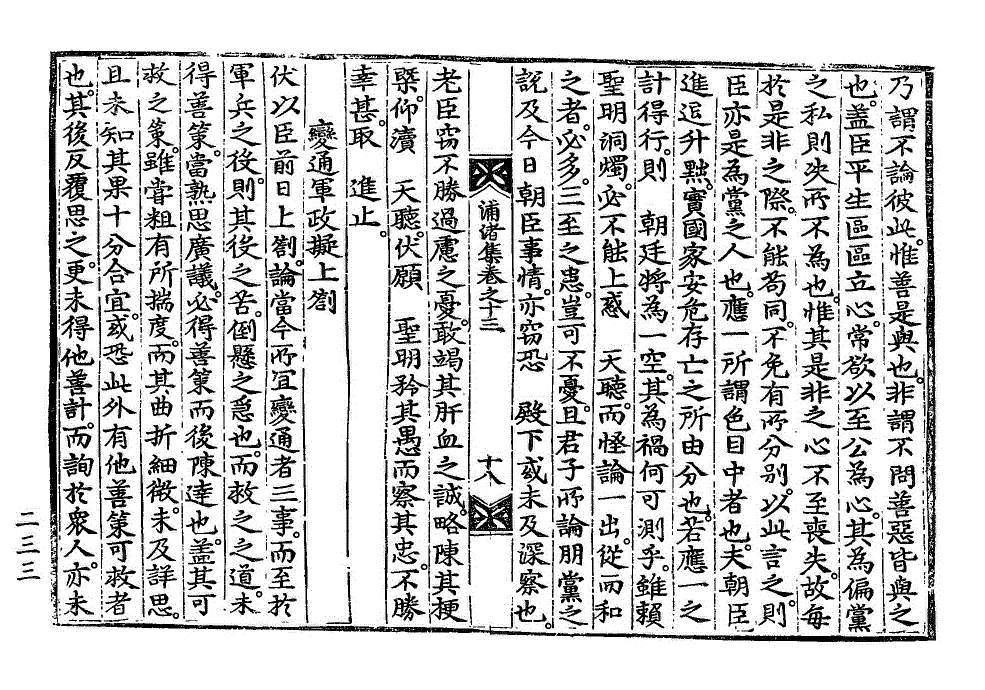 乃谓不论彼此。惟善是与也。非谓不问善恶皆与之也。盖臣平生区区立心。常欲以至公为心。其为偏党之私则决所不为也。惟其是非之心不至丧失。故每于是非之际。不能苟同。不免有所分别。以此言之。则臣亦是为党之人也。应一所谓色目中者也。夫朝臣进退升黜。实国家安危存亡之所由分也。若应一之计得行。则 朝廷将为一空。其为祸何可测乎。虽赖圣明洞烛。必不能上惑 天听。而怪论一出。从而和之者。必多。三至之患。岂可不忧。且君子所论朋党之说及今日朝臣事情。亦窃恐 殿下或未及深察也。老臣窃不胜过虑之忧。敢竭其肝血之诚。略陈其梗槩。仰渎 天听。伏愿 圣明矜其愚而察其忠。不胜幸甚。取 进止。
乃谓不论彼此。惟善是与也。非谓不问善恶皆与之也。盖臣平生区区立心。常欲以至公为心。其为偏党之私则决所不为也。惟其是非之心不至丧失。故每于是非之际。不能苟同。不免有所分别。以此言之。则臣亦是为党之人也。应一所谓色目中者也。夫朝臣进退升黜。实国家安危存亡之所由分也。若应一之计得行。则 朝廷将为一空。其为祸何可测乎。虽赖圣明洞烛。必不能上惑 天听。而怪论一出。从而和之者。必多。三至之患。岂可不忧。且君子所论朋党之说及今日朝臣事情。亦窃恐 殿下或未及深察也。老臣窃不胜过虑之忧。敢竭其肝血之诚。略陈其梗槩。仰渎 天听。伏愿 圣明矜其愚而察其忠。不胜幸甚。取 进止。变通军政拟上劄
伏以臣前日上劄。论当今所宜变通者三事。而至于军兵之役。则其役之苦。倒悬之急也。而救之之道。未得善策。当熟思广议。必得善策而后陈达也。盖其可救之策。虽尝粗有所揣度。而其曲折细微。未及详思。且未知其果十分合宜。或恐此外有他善策可救者也。其后反覆思之。更未得他善计。而询于众人。亦未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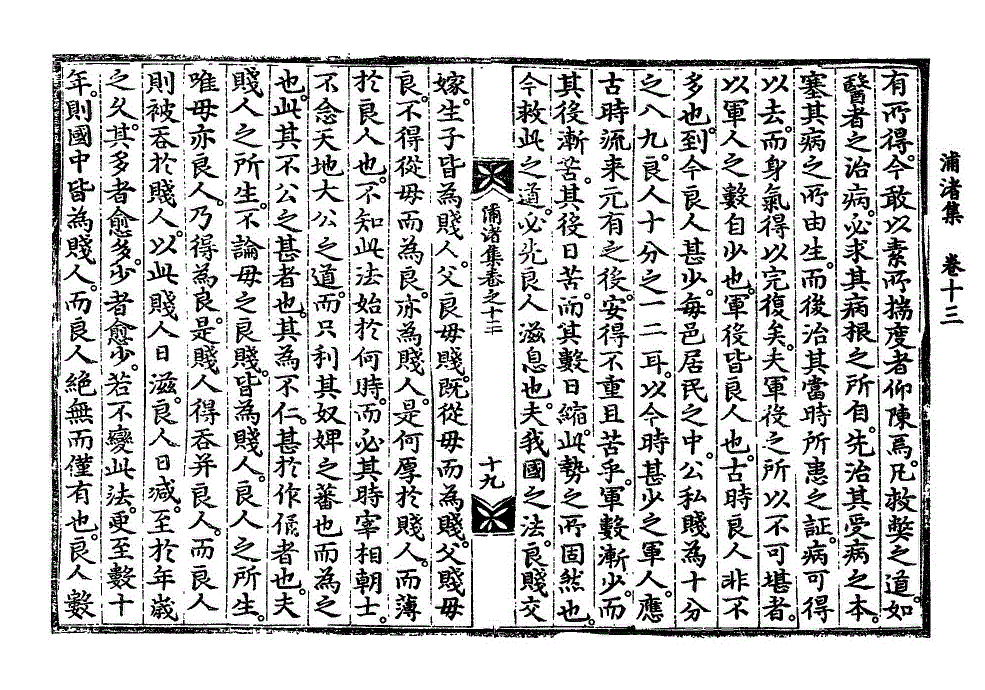 有所得。今敢以素所揣度者仰陈焉。凡救弊之道。如医者之治病。必求其病根之所自。先治其受病之本。塞其病之所由生。而后治其当时所患之證。病可得以去。而身气得以完复矣。夫军役之所以不可堪者。以军人之数自少也。军役皆良人也。古时良人非不多也。到今良人甚少。每邑居民之中。公私贱为十分之八九。良人十分之一二耳。以今时甚少之军人。应古时流来元有之役。安得不重且苦乎。军数渐少。而其役渐苦。其役日苦。而其数日缩。此势之所固然也。今救此之道。必先良人滋息也。夫我国之法。良贱交嫁。生子皆为贱人。父良母贱。既从母而为贱。父贱母良。不得从母而为良。亦为贱人。是何厚于贱人。而薄于良人也。不知此法始于何时。而必其时宰相朝士。不念天地大公之道。而只利其奴婢之蕃也而为之也。此其不公之甚者也。其为不仁。甚于作俑者也。夫贱人之所生。不论母之良贱。皆为贱人。良人之所生。唯母亦良人。乃得为良。是贱人得吞并良人。而良人则被吞于贱人。以此贱人日滋。良人日减。至于年岁之久。其多者愈多。少者愈少。若不变此法。更至数十年。则国中皆为贱人。而良人绝无而仅有也。良人数
有所得。今敢以素所揣度者仰陈焉。凡救弊之道。如医者之治病。必求其病根之所自。先治其受病之本。塞其病之所由生。而后治其当时所患之證。病可得以去。而身气得以完复矣。夫军役之所以不可堪者。以军人之数自少也。军役皆良人也。古时良人非不多也。到今良人甚少。每邑居民之中。公私贱为十分之八九。良人十分之一二耳。以今时甚少之军人。应古时流来元有之役。安得不重且苦乎。军数渐少。而其役渐苦。其役日苦。而其数日缩。此势之所固然也。今救此之道。必先良人滋息也。夫我国之法。良贱交嫁。生子皆为贱人。父良母贱。既从母而为贱。父贱母良。不得从母而为良。亦为贱人。是何厚于贱人。而薄于良人也。不知此法始于何时。而必其时宰相朝士。不念天地大公之道。而只利其奴婢之蕃也而为之也。此其不公之甚者也。其为不仁。甚于作俑者也。夫贱人之所生。不论母之良贱。皆为贱人。良人之所生。唯母亦良人。乃得为良。是贱人得吞并良人。而良人则被吞于贱人。以此贱人日滋。良人日减。至于年岁之久。其多者愈多。少者愈少。若不变此法。更至数十年。则国中皆为贱人。而良人绝无而仅有也。良人数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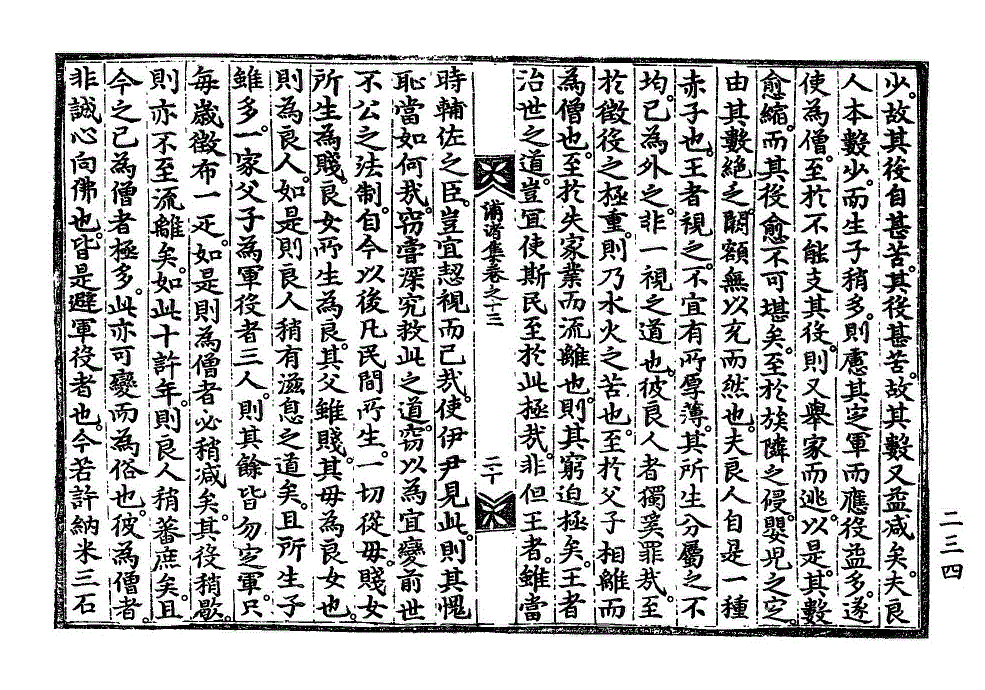 少。故其役自甚苦。其役甚苦。故其数又益减矣。夫良人本数少。而生子稍多。则虑其定军而应役益多。遂使为僧。至于不能支其役。则又举家而逃。以是。其数愈缩。而其役愈不可堪矣。至于族邻之侵。婴儿之定。由其数绝乏。阙额无以充而然也。夫良人自是一种赤子也。王者视之。不宜有所厚薄。其所生分属之不均。已为外之。非一视之道也。彼良人者独奚罪哉。至于徵役之极重。则乃水火之苦也。至于父子相离而为僧也。至于失家业而流离也。则其穷迫极矣。王者治世之道。岂宜使斯民至于此极哉。非但王者。虽当时辅佐之臣。岂宜恝视而已哉。使伊尹见此。则其愧耻当如何哉。窃尝深究救此之道。窃以为宜变前世不公之法制。自今以后凡民间所生。一切从母。贱女所生为贱。良女所生为良。其父虽贱。其母为良女也。则为良人。如是则良人稍有滋息之道矣。且所生子虽多。一家父子为军役者三人。则其馀皆勿定军。只每岁徵布一疋。如是则为僧者必稍减矣。其役稍歇。则亦不至流离矣。如此十许年。则良人稍蕃庶矣。且今之已为僧者极多。此亦可变而为俗也。彼为僧者。非诚心向佛也。皆是避军役者也。今若许纳米三石
少。故其役自甚苦。其役甚苦。故其数又益减矣。夫良人本数少。而生子稍多。则虑其定军而应役益多。遂使为僧。至于不能支其役。则又举家而逃。以是。其数愈缩。而其役愈不可堪矣。至于族邻之侵。婴儿之定。由其数绝乏。阙额无以充而然也。夫良人自是一种赤子也。王者视之。不宜有所厚薄。其所生分属之不均。已为外之。非一视之道也。彼良人者独奚罪哉。至于徵役之极重。则乃水火之苦也。至于父子相离而为僧也。至于失家业而流离也。则其穷迫极矣。王者治世之道。岂宜使斯民至于此极哉。非但王者。虽当时辅佐之臣。岂宜恝视而已哉。使伊尹见此。则其愧耻当如何哉。窃尝深究救此之道。窃以为宜变前世不公之法制。自今以后凡民间所生。一切从母。贱女所生为贱。良女所生为良。其父虽贱。其母为良女也。则为良人。如是则良人稍有滋息之道矣。且所生子虽多。一家父子为军役者三人。则其馀皆勿定军。只每岁徵布一疋。如是则为僧者必稍减矣。其役稍歇。则亦不至流离矣。如此十许年。则良人稍蕃庶矣。且今之已为僧者极多。此亦可变而为俗也。彼为僧者。非诚心向佛也。皆是避军役者也。今若许纳米三石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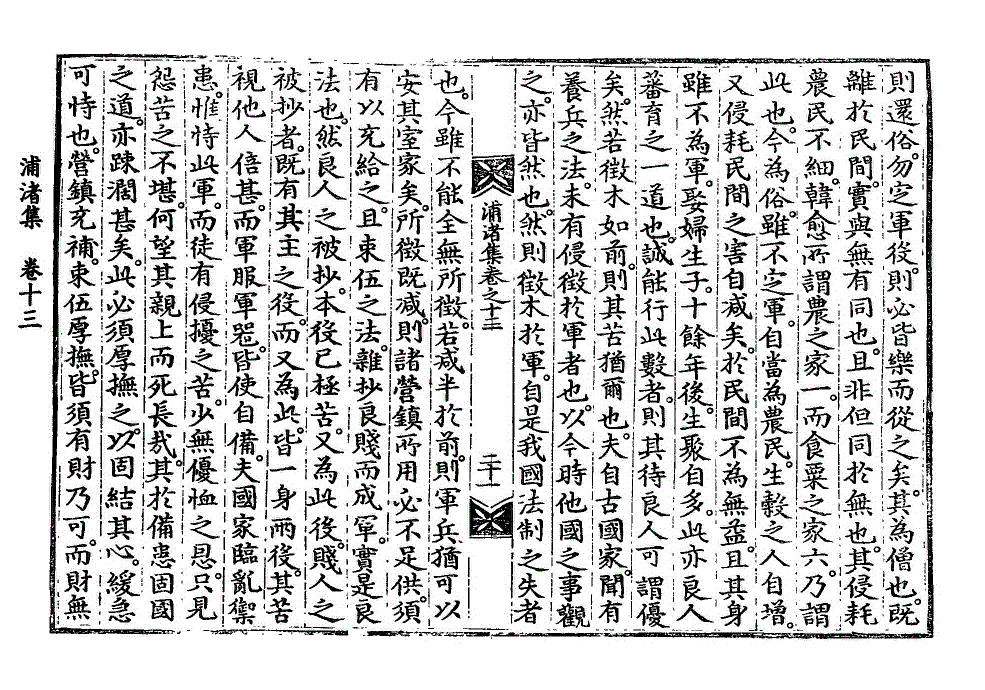 则还俗。勿定军役。则必皆乐而从之矣。其为僧也。既离于民间。实与无有同也。且非但同于无也。其侵耗农民不细。韩愈所谓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乃谓此也。今为俗。虽不定军。自当为农民。生谷之人自增。又侵耗民间之害自减矣。于民间不为无益。且其身虽不为军。娶妇生子。十馀年后。生聚自多。此亦良人蕃育之一道也。诚能行此数者。则其待良人可谓优矣。然若徵木如前。则其苦犹尔也。夫自古国家。闻有养兵之法。未有侵徵于军者也。以今时他国之事观之。亦皆然也。然则徵木于军。自是我国法制之失者也。今虽不能全无所徵。若减半于前。则军兵犹可以安其室家矣。所徵既减。则诸营镇所用必不足供。须有以充给之。且束伍之法。杂抄良贱而成军。实是良法也。然良人之被抄。本役已极苦。又为此役。贱人之被抄者。既有其主之役。而又为此。皆一身两役。其苦视他人倍甚。而军服军器。皆使自备。夫国家临乱御患。惟恃此军。而徒有侵扰之苦。少无优恤之恩。只见怨苦之不堪。何望其亲上而死长哉。其于备患固国之道。亦疏阔甚矣。此必须厚抚之。以固结其心。缓急可恃也。营镇充补。束伍厚抚。皆须有财乃可。而财无
则还俗。勿定军役。则必皆乐而从之矣。其为僧也。既离于民间。实与无有同也。且非但同于无也。其侵耗农民不细。韩愈所谓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乃谓此也。今为俗。虽不定军。自当为农民。生谷之人自增。又侵耗民间之害自减矣。于民间不为无益。且其身虽不为军。娶妇生子。十馀年后。生聚自多。此亦良人蕃育之一道也。诚能行此数者。则其待良人可谓优矣。然若徵木如前。则其苦犹尔也。夫自古国家。闻有养兵之法。未有侵徵于军者也。以今时他国之事观之。亦皆然也。然则徵木于军。自是我国法制之失者也。今虽不能全无所徵。若减半于前。则军兵犹可以安其室家矣。所徵既减。则诸营镇所用必不足供。须有以充给之。且束伍之法。杂抄良贱而成军。实是良法也。然良人之被抄。本役已极苦。又为此役。贱人之被抄者。既有其主之役。而又为此。皆一身两役。其苦视他人倍甚。而军服军器。皆使自备。夫国家临乱御患。惟恃此军。而徒有侵扰之苦。少无优恤之恩。只见怨苦之不堪。何望其亲上而死长哉。其于备患固国之道。亦疏阔甚矣。此必须厚抚之。以固结其心。缓急可恃也。营镇充补。束伍厚抚。皆须有财乃可。而财无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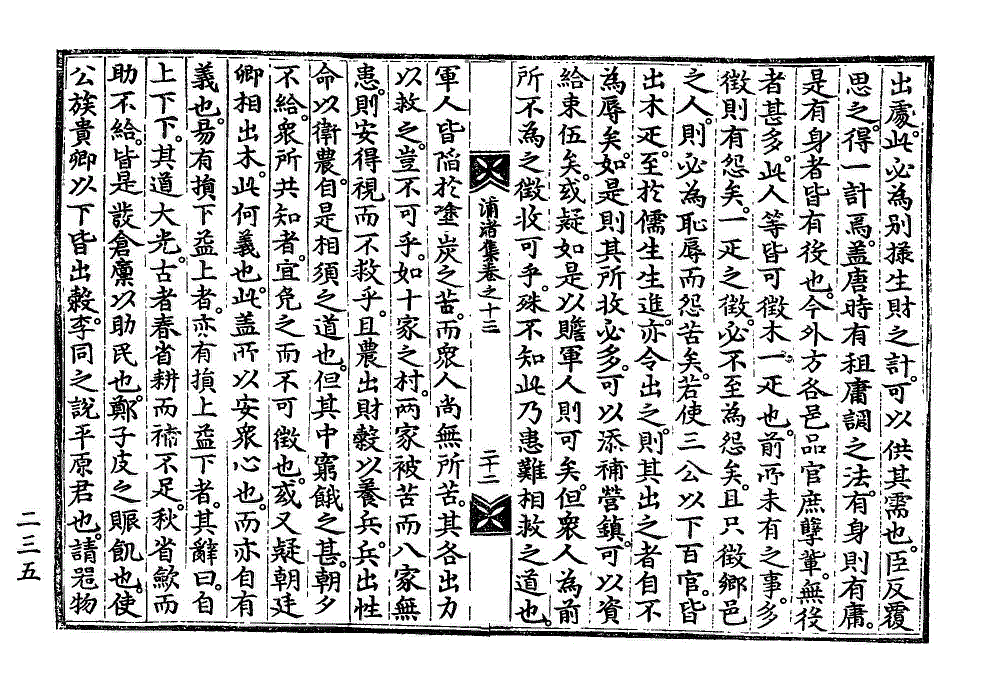 出处。此必为别样生财之计。可以供其需也。臣反覆思之。得一计焉。盖唐时有租庸调之法。有身则有庸。是有身者皆有役也。今外方各邑品官庶孽辈。无役者甚多。此人等皆可徵木一疋也。前所未有之事。多徵则有怨矣。一疋之徵。必不至为怨矣。且只徵乡邑之人。则必为耻辱而怨苦矣。若使三公以下百官。皆出木疋。至于儒生生进。亦令出之。则其出之者自不为辱矣。如是则其所收必多。可以添补营镇。可以资给束伍矣。或疑如是以赡军人则可矣。但众人为前所不为之徵收可乎。殊不知此乃患难相救之道也。军人皆陷于涂炭之苦。而众人尚无所苦。其各出力以救之。岂不可乎。如十家之村。两家被苦而八家无患。则安得视而不救乎。且农出财谷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自是相须之道也。但其中穷饿之甚。朝夕不给。众所共知者。宜免之而不可徵也。或又疑朝廷卿相出木。此何义也。此盖所以安众心也。而亦自有义也。易有损下益上者。亦有损上益下者。其辞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古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皆是发仓廪以助民也。郑子皮之赈饥也。使公族贵卿以下皆出谷。李同之说平原君也。请器物
出处。此必为别样生财之计。可以供其需也。臣反覆思之。得一计焉。盖唐时有租庸调之法。有身则有庸。是有身者皆有役也。今外方各邑品官庶孽辈。无役者甚多。此人等皆可徵木一疋也。前所未有之事。多徵则有怨矣。一疋之徵。必不至为怨矣。且只徵乡邑之人。则必为耻辱而怨苦矣。若使三公以下百官。皆出木疋。至于儒生生进。亦令出之。则其出之者自不为辱矣。如是则其所收必多。可以添补营镇。可以资给束伍矣。或疑如是以赡军人则可矣。但众人为前所不为之徵收可乎。殊不知此乃患难相救之道也。军人皆陷于涂炭之苦。而众人尚无所苦。其各出力以救之。岂不可乎。如十家之村。两家被苦而八家无患。则安得视而不救乎。且农出财谷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自是相须之道也。但其中穷饿之甚。朝夕不给。众所共知者。宜免之而不可徵也。或又疑朝廷卿相出木。此何义也。此盖所以安众心也。而亦自有义也。易有损下益上者。亦有损上益下者。其辞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古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皆是发仓廪以助民也。郑子皮之赈饥也。使公族贵卿以下皆出谷。李同之说平原君也。请器物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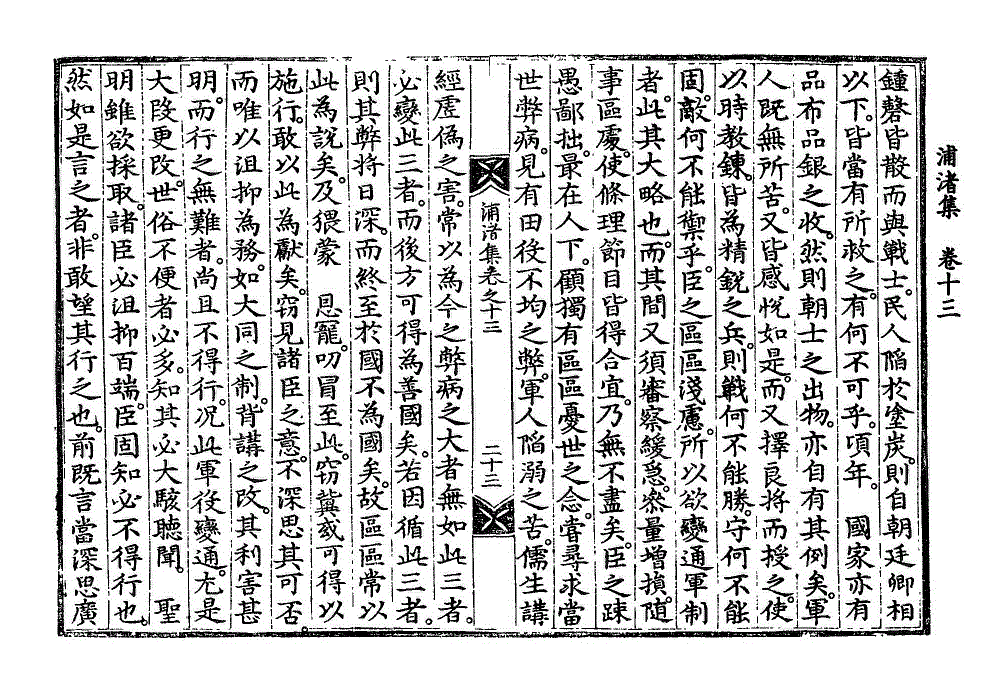 钟磬皆散而与战士。民人陷于涂炭。则自朝廷卿相以下。皆当有所救之。有何不可乎。顷年。 国家亦有品布品银之收。然则朝士之出物。亦自有其例矣。军人既无所苦。又皆感悦如是。而又择良将而授之。使以时教鍊。皆为精锐之兵。则战何不能胜。守何不能固。敌何不能御乎。臣之区区浅虑。所以欲变通军制者。此其大略也。而其间又须审察缓急。参量增损。随事区处。使条理节目皆得合宜。乃无不尽矣。臣之疏愚鄙拙。最在人下。顾独有区区忧世之念。尝寻求当世弊病。见有田役不均之弊。军人陷溺之苦。儒生讲经虚伪之害。常以为今之弊病之大者无如此三者。必变此三者。而后方可得为善国矣。若因循此三者。则其弊将日深。而终至于国不为国矣。故区区常以此为说矣。及猥蒙 恩宠。叨冒至此。窃冀或可得以施行。敢以此为献矣。窃见诸臣之意。不深思其可否。而唯以沮抑为务。如大同之制。背讲之改。其利害甚明。而行之无难者。尚且不得行。况此军役变通。尤是大段更改。世俗不便者必多。知其必大骇听闻。 圣明虽欲采取。诸臣必沮抑百端。臣固知必不得行也。然如是言之者。非敢望其行之也。前既言当深思广
钟磬皆散而与战士。民人陷于涂炭。则自朝廷卿相以下。皆当有所救之。有何不可乎。顷年。 国家亦有品布品银之收。然则朝士之出物。亦自有其例矣。军人既无所苦。又皆感悦如是。而又择良将而授之。使以时教鍊。皆为精锐之兵。则战何不能胜。守何不能固。敌何不能御乎。臣之区区浅虑。所以欲变通军制者。此其大略也。而其间又须审察缓急。参量增损。随事区处。使条理节目皆得合宜。乃无不尽矣。臣之疏愚鄙拙。最在人下。顾独有区区忧世之念。尝寻求当世弊病。见有田役不均之弊。军人陷溺之苦。儒生讲经虚伪之害。常以为今之弊病之大者无如此三者。必变此三者。而后方可得为善国矣。若因循此三者。则其弊将日深。而终至于国不为国矣。故区区常以此为说矣。及猥蒙 恩宠。叨冒至此。窃冀或可得以施行。敢以此为献矣。窃见诸臣之意。不深思其可否。而唯以沮抑为务。如大同之制。背讲之改。其利害甚明。而行之无难者。尚且不得行。况此军役变通。尤是大段更改。世俗不便者必多。知其必大骇听闻。 圣明虽欲采取。诸臣必沮抑百端。臣固知必不得行也。然如是言之者。非敢望其行之也。前既言当深思广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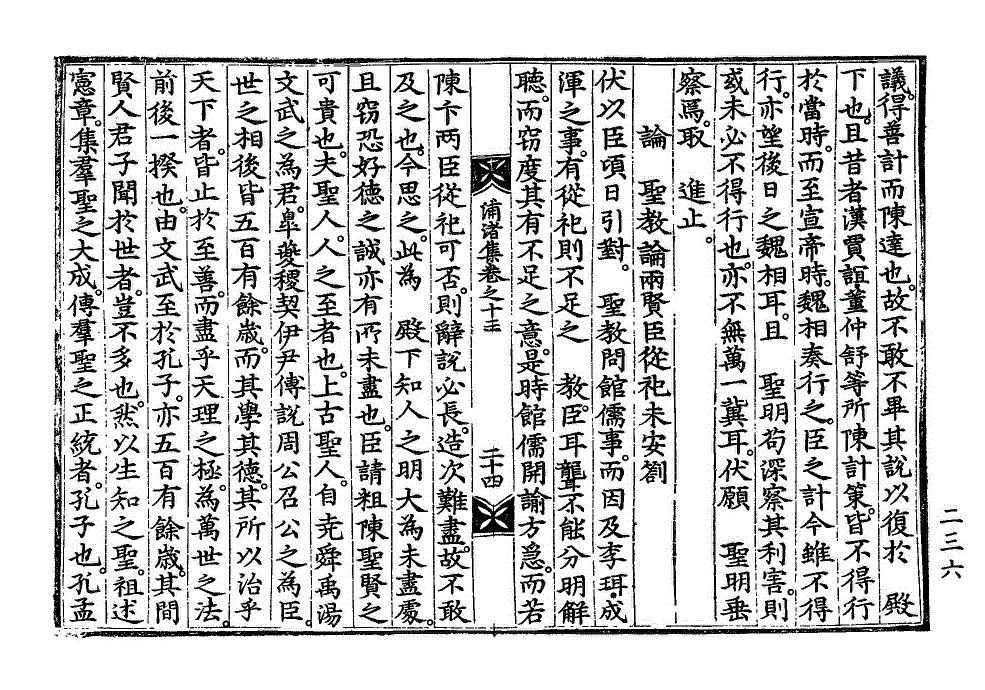 议。得善计而陈达也。故不敢不毕其说以复于 殿下也。且昔者汉贾谊,董仲舒等所陈计策。皆不得行于当时。而至宣帝时。魏相奏行之。臣之计今虽不得行。亦望后日之魏相耳。且 圣明苟深察其利害。则或未必不得行也。亦不无万一冀耳。伏愿 圣明垂察焉。取 进止。
议。得善计而陈达也。故不敢不毕其说以复于 殿下也。且昔者汉贾谊,董仲舒等所陈计策。皆不得行于当时。而至宣帝时。魏相奏行之。臣之计今虽不得行。亦望后日之魏相耳。且 圣明苟深察其利害。则或未必不得行也。亦不无万一冀耳。伏愿 圣明垂察焉。取 进止。论 圣教论两贤臣从祀未安劄
伏以臣顷日引对。 圣教问馆儒事。而因及李珥,成浑之事。有从祀则不足之 教。臣耳聋不能分明解听。而窃度其有不足之意。是时馆儒开谕方急。而若陈卞两臣从祀可否。则辞说必长。造次难尽。故不敢及之也。今思之。此为 殿下知人之明大为未尽处。且窃恐好德之诚亦有所未尽也。臣请粗陈圣贤之可贵也。夫圣人。人之至者也。上古圣人。自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君。皋夔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之为臣。世之相后皆五百有馀岁。而其学其德。其所以治乎天下者。皆止于至善。而尽乎天理之极。为万世之法。前后一揆也。由文武至于孔子。亦五百有馀岁。其间贤人君子闻于世者。岂不多也。然以生知之圣。祖述宪章。集群圣之大成。传群圣之正统者。孔子也。孔孟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37H 页
 之后千数百年。而得程朱子焉。其间贤士君子亦非不多也。然能寻究遗经之中。深得圣人之意。其知识践行。脱然拔乎流俗。一以圣人为法。自程子始。以至朱子而大成焉。天之生圣贤。其不数如此。而人文教化。赖圣贤而明焉。然则圣贤者。岂非世之至可贵者乎。东方自前朝。文学则可谓盛矣。惟义理之学未盛。至 本朝始盛。斯亦天启文明之运。如宋之聚奎也。臣尝闻故参赞白仁杰。在 宣庙朝进言曰。东方道学。自郑梦周,金宏弼始有渊源。至赵光祖。以杰出之才。阐明程朱之学。循蹈规矩。非礼不动。大励名节。兴起斯文。得君致理。脩行德政。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奸臣构祸。竟致冤死。朝野之痛。久而愈新。谓宜追奖真儒。从祀 文庙。又曰。我国从祀之贤。惟郑梦周协于士望。其馀薛聪,崔致远,安裕辈。皆出光祖下远甚。又李珥启曰。欲明教化。必须尊奖先贤。使后学有所矜式。我 朝贤者。虽未得悉入祀典。如赵光祖倡明道学。李滉沈潜理窟。亟宜先许从祀。以振士望。以此观之。则 本朝先贤。惟赵光祖,李滉为最盛。赵光祖,李滉之外。未有如李珥,成浑者也。此非臣之言也。向来先辈之言皆然也。且昔宰我,子贡,有若。言生民
之后千数百年。而得程朱子焉。其间贤士君子亦非不多也。然能寻究遗经之中。深得圣人之意。其知识践行。脱然拔乎流俗。一以圣人为法。自程子始。以至朱子而大成焉。天之生圣贤。其不数如此。而人文教化。赖圣贤而明焉。然则圣贤者。岂非世之至可贵者乎。东方自前朝。文学则可谓盛矣。惟义理之学未盛。至 本朝始盛。斯亦天启文明之运。如宋之聚奎也。臣尝闻故参赞白仁杰。在 宣庙朝进言曰。东方道学。自郑梦周,金宏弼始有渊源。至赵光祖。以杰出之才。阐明程朱之学。循蹈规矩。非礼不动。大励名节。兴起斯文。得君致理。脩行德政。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奸臣构祸。竟致冤死。朝野之痛。久而愈新。谓宜追奖真儒。从祀 文庙。又曰。我国从祀之贤。惟郑梦周协于士望。其馀薛聪,崔致远,安裕辈。皆出光祖下远甚。又李珥启曰。欲明教化。必须尊奖先贤。使后学有所矜式。我 朝贤者。虽未得悉入祀典。如赵光祖倡明道学。李滉沈潜理窟。亟宜先许从祀。以振士望。以此观之。则 本朝先贤。惟赵光祖,李滉为最盛。赵光祖,李滉之外。未有如李珥,成浑者也。此非臣之言也。向来先辈之言皆然也。且昔宰我,子贡,有若。言生民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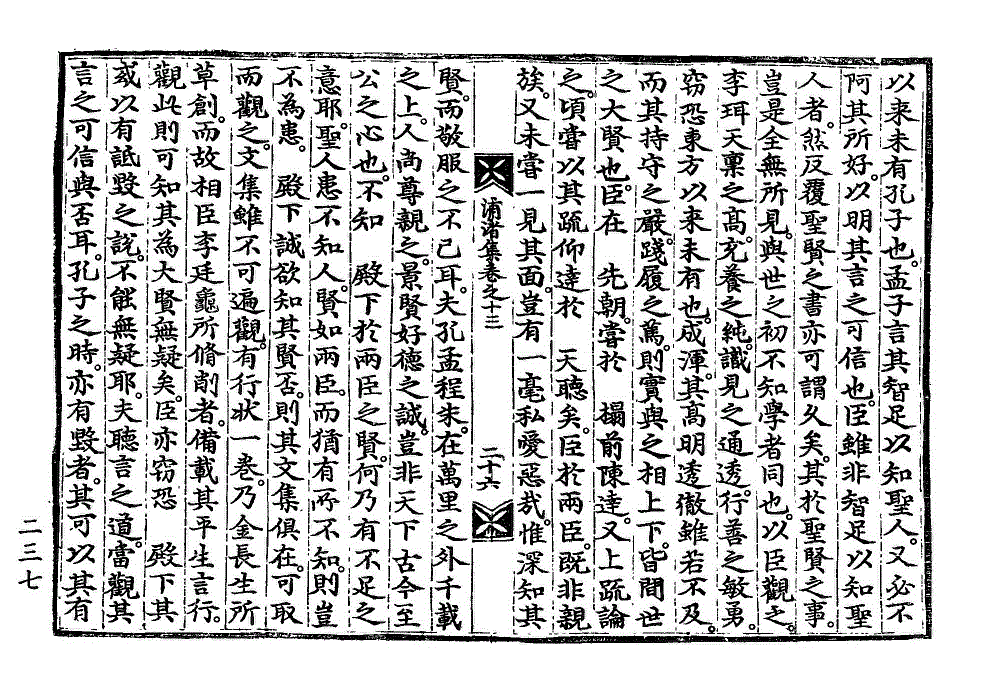 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言其智足以知圣人。又必不阿其所好。以明其言之可信也。臣虽非智足以知圣人者。然反覆圣贤之书亦可谓久矣。其于圣贤之事。岂是全无所见。与世之初不知学者同也。以臣观之。李珥天禀之高。充养之纯。识见之通透。行善之敏勇。窃恐东方以来未有也。成浑。其高明透彻虽若不及。而其持守之严。践履之笃。则实与之相上下。皆间世之大贤也。臣在 先朝。尝于 榻前陈达。又上疏论之。顷尝以其疏仰达于 天听矣。臣于两臣。既非亲族。又未尝一见其面。岂有一毫私爱恶哉。惟深知其贤。而敬服之不已耳。夫孔孟程朱。在万里之外千载之上。人尚尊亲之。景贤好德之诚。岂非天下古今至公之心也。不知 殿下于两臣之贤。何乃有不足之意耶。圣人患不知人。贤如两臣。而犹有所不知。则岂不为患。 殿下诚欲知其贤否。则其文集俱在。可取而观之。文集虽不可遍观。有行状一卷。乃金长生所草创。而故相臣李廷龟所脩削者。备载其平生言行。观此则可知其为大贤无疑矣。臣亦窃恐 殿下其或以有诋毁之说。不能无疑耶。夫听言之道。当观其言之可信与否耳。孔子之时。亦有毁者。其可以其有
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言其智足以知圣人。又必不阿其所好。以明其言之可信也。臣虽非智足以知圣人者。然反覆圣贤之书亦可谓久矣。其于圣贤之事。岂是全无所见。与世之初不知学者同也。以臣观之。李珥天禀之高。充养之纯。识见之通透。行善之敏勇。窃恐东方以来未有也。成浑。其高明透彻虽若不及。而其持守之严。践履之笃。则实与之相上下。皆间世之大贤也。臣在 先朝。尝于 榻前陈达。又上疏论之。顷尝以其疏仰达于 天听矣。臣于两臣。既非亲族。又未尝一见其面。岂有一毫私爱恶哉。惟深知其贤。而敬服之不已耳。夫孔孟程朱。在万里之外千载之上。人尚尊亲之。景贤好德之诚。岂非天下古今至公之心也。不知 殿下于两臣之贤。何乃有不足之意耶。圣人患不知人。贤如两臣。而犹有所不知。则岂不为患。 殿下诚欲知其贤否。则其文集俱在。可取而观之。文集虽不可遍观。有行状一卷。乃金长生所草创。而故相臣李廷龟所脩削者。备载其平生言行。观此则可知其为大贤无疑矣。臣亦窃恐 殿下其或以有诋毁之说。不能无疑耶。夫听言之道。当观其言之可信与否耳。孔子之时。亦有毁者。其可以其有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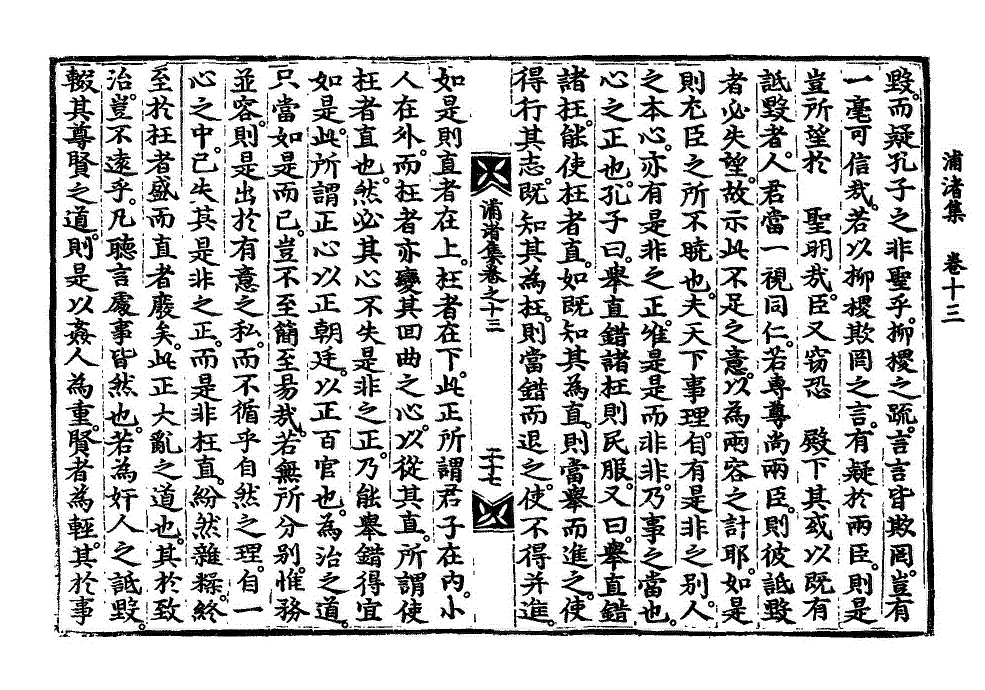 毁。而疑孔子之非圣乎。柳㮨之疏。言言皆欺罔。岂有一毫可信哉。若以柳㮨欺罔之言。有疑于两臣。则是岂所望于 圣明哉。臣又窃恐 殿下其或以既有诋毁者。人君当一视同仁。若专尊尚两臣。则彼诋毁者必失望。故示此不足之意。以为两容之计耶。如是则尤臣之所不晓也。夫天下事理。自有是非之别。人之本心。亦有是非之正。唯是是而非非。乃事之当也。心之正也。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又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如既知其为直。则当举而进之。使得行其志。既知其为枉。则当错而退之。使不得并进。如是则直者在上。枉者在下。此正所谓君子在内。小人在外。而枉者亦变其回曲之心。以从其直。所谓使枉者直也。然必其心不失是非之正。乃能举错得宜如是。此所谓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也。为治之道。只当如是而已。岂不至简至易哉。若无所分别。惟务并容。则是出于有意之私。而不循乎自然之理。自一心之中。已失其是非之正。而是非枉直。纷然杂糅。终至于枉者盛而直者废矣。此正大乱之道也。其于致治。岂不远乎。凡听言处事皆然也。若为奸人之诋毁。辍其尊贤之道。则是以奸人为重。贤者为轻。其于事
毁。而疑孔子之非圣乎。柳㮨之疏。言言皆欺罔。岂有一毫可信哉。若以柳㮨欺罔之言。有疑于两臣。则是岂所望于 圣明哉。臣又窃恐 殿下其或以既有诋毁者。人君当一视同仁。若专尊尚两臣。则彼诋毁者必失望。故示此不足之意。以为两容之计耶。如是则尤臣之所不晓也。夫天下事理。自有是非之别。人之本心。亦有是非之正。唯是是而非非。乃事之当也。心之正也。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又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如既知其为直。则当举而进之。使得行其志。既知其为枉。则当错而退之。使不得并进。如是则直者在上。枉者在下。此正所谓君子在内。小人在外。而枉者亦变其回曲之心。以从其直。所谓使枉者直也。然必其心不失是非之正。乃能举错得宜如是。此所谓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也。为治之道。只当如是而已。岂不至简至易哉。若无所分别。惟务并容。则是出于有意之私。而不循乎自然之理。自一心之中。已失其是非之正。而是非枉直。纷然杂糅。终至于枉者盛而直者废矣。此正大乱之道也。其于致治。岂不远乎。凡听言处事皆然也。若为奸人之诋毁。辍其尊贤之道。则是以奸人为重。贤者为轻。其于事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38L 页
 理。岂当然乎。伏愿 圣明深察人心本然。是非之正。不可以私意计较有所变易。而处事之道。皆有自然之理。当循其自然。行所无事。一于天理之正。则古之圣帝明王所以致治之道。不过如是而已也。远近臣民。孰不咸仰一哉之心乎。臣伏见 殿下于两臣。有不足之意。窃恐 圣志犹未定。窃不胜忧虑之深。故敢罄竭区区所怀。以冀有所省察也。无任悚惧之至。取 进止。
理。岂当然乎。伏愿 圣明深察人心本然。是非之正。不可以私意计较有所变易。而处事之道。皆有自然之理。当循其自然。行所无事。一于天理之正。则古之圣帝明王所以致治之道。不过如是而已也。远近臣民。孰不咸仰一哉之心乎。臣伏见 殿下于两臣。有不足之意。窃恐 圣志犹未定。窃不胜忧虑之深。故敢罄竭区区所怀。以冀有所省察也。无任悚惧之至。取 进止。因 圣批辞职劄
伏以臣自少深服李珥,成浑两臣之贤。其悦而慕之。无异于亲承教诲。而仰之无异于古之圣贤。区区朴愚之性。自有知以来。所闻所知如此。故其寻常言论。不能变其所知以欺其心。此臣固滞之性所以终身守株。而不知变者也。伏见 圣教于两臣。有不足之意。窃恐 殿下知人之明有所未尽。而好贤之诚亦有所未至也。知人未尽。好贤未至。则其为害岂不大乎。若于此默然而已。则是欺 殿下也。岂事君以忠之道乎。以是。区区之心。不能自安。敢略陈两臣贤德之实。仰冀 省察。此只是为 圣明愿明两臣而已。岂有一毫他意乎。伏承 圣批。乃曰。勿为纷扰者之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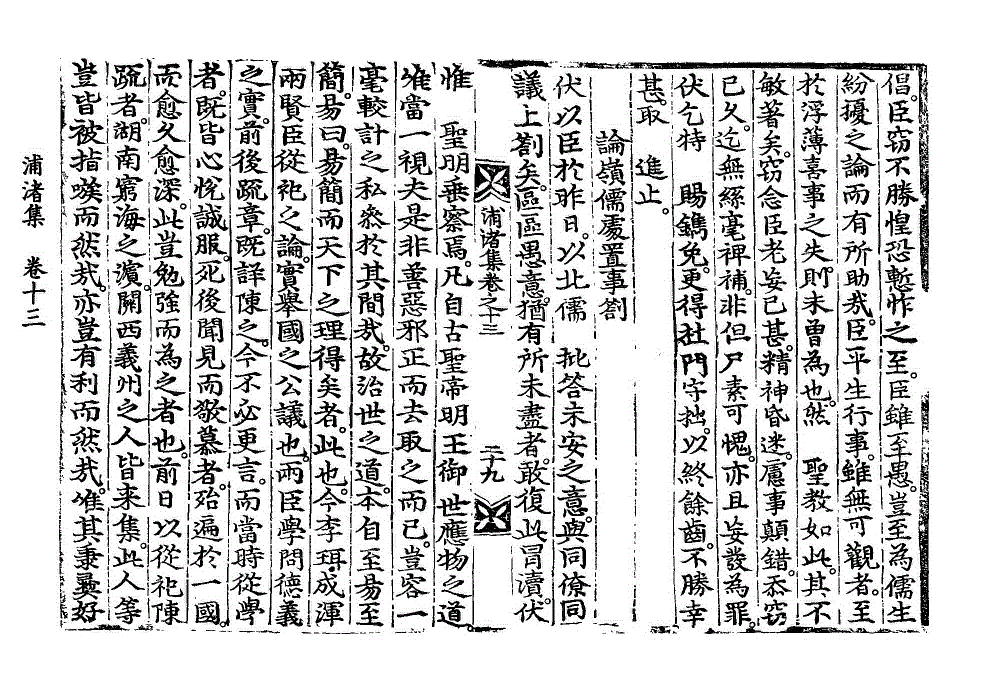 倡。臣窃不胜惶恐惭怍之至。臣虽至愚。岂至为儒生纷扰之论而有所助哉。臣平生行事。虽无可观者。至于浮薄喜事之失。则未曾为也。然 圣教如此。其不敏著矣。窃念臣老妄已甚。精神昏迷。虑事颠错。忝窃已久。迄无丝毫裨补。非但尸素可愧。亦且妄发为罪。伏乞特 赐镌免。更得杜门守拙。以终馀齿。不胜幸甚。取 进止。
倡。臣窃不胜惶恐惭怍之至。臣虽至愚。岂至为儒生纷扰之论而有所助哉。臣平生行事。虽无可观者。至于浮薄喜事之失。则未曾为也。然 圣教如此。其不敏著矣。窃念臣老妄已甚。精神昏迷。虑事颠错。忝窃已久。迄无丝毫裨补。非但尸素可愧。亦且妄发为罪。伏乞特 赐镌免。更得杜门守拙。以终馀齿。不胜幸甚。取 进止。论岭儒处置事劄
伏以臣于昨日。以北儒 批答未安之意。与同僚同议上劄矣。区区愚意。犹有所未尽者。敢复此冒渎。伏惟 圣明垂察焉。凡自古圣帝明王御世应物之道。唯当一视夫是非善恶邪正而去取之而已。岂容一毫较计之私参于其间哉。故治世之道。本自至易至简。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此也。今李珥,成浑两贤臣从祀之论。实举国之公议也。两臣学问德义之实。前后疏章。既详陈之。今不必更言。而当时从学者。既皆心悦诚服。死后闻见而敬慕者。殆遍于一国。而愈久愈深。此岂勉强而为之者也。前日以从祀陈疏者。湖南穷海之滨。关西义州之人皆来集。此人等岂皆被指嗾而然哉。亦岂有利而然哉。唯其秉彝好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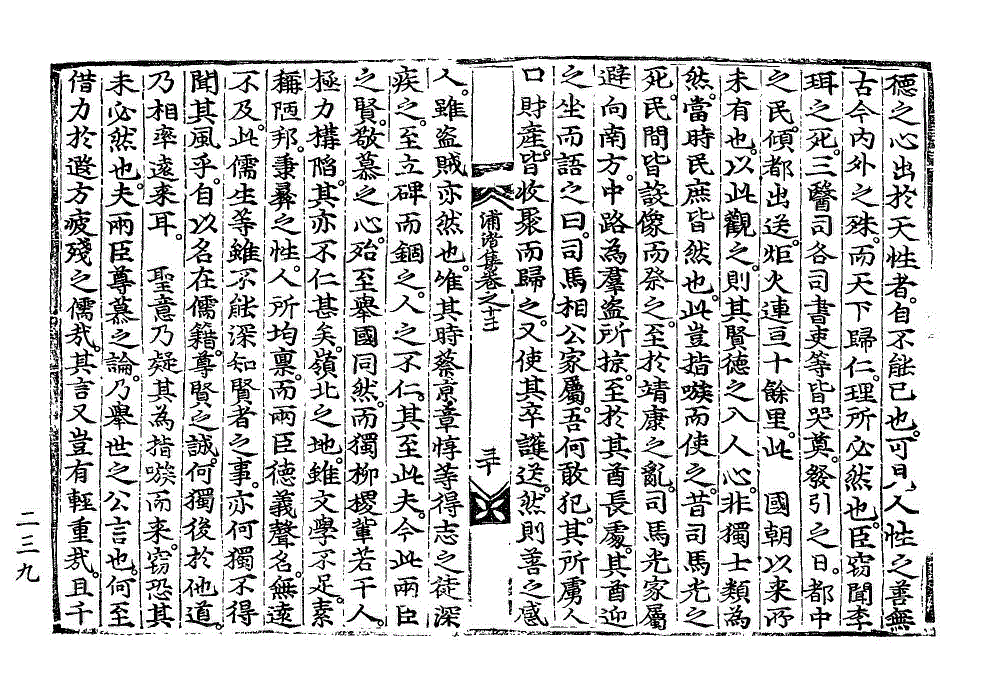 德之心出于天性者。自不能已也。可见人性之善无古今内外之殊。而天下归仁。理所必然也。臣窃闻李珥之死。三医司各司书吏等皆哭奠。发引之日。都中之民。倾都出送。炬火连亘十馀里。此 国朝以来所未有也。以此观之。则其贤德之入人心。非独士类为然。当时民庶皆然也。此岂指嗾而使之。昔司马光之死。民间皆设像而祭之。至于靖康之乱。司马光家属避向南方。中路为群盗所掠。至于其酋长处。其酋迎之坐而语之曰。司马相公家属。吾何敢犯。其所虏人口财产。皆收聚而归之。又使其卒护送。然则善之感人。虽盗贼亦然也。唯其时蔡京,章惇等得志之徒深疾之。至立碑而锢之。人之不仁。其至此夫。今此两臣之贤。敬慕之心。殆至举国同然。而独柳㮨辈若干人。极力构陷。其亦不仁甚矣。岭北之地。虽文学不足。素称陋邦。秉彝之性。人所均禀。而两臣德义声名。无远不及。此儒生等虽不能深知贤者之事。亦何独不得闻其风乎。自以名在儒籍。尊贤之诚。何独后于他道。乃相率远来耳。 圣意乃疑其为指嗾而来。窃恐其未必然也。夫两臣尊慕之论。乃举世之公言也。何至借力于遐方疲残之儒哉。其言又岂有轻重哉。且千
德之心出于天性者。自不能已也。可见人性之善无古今内外之殊。而天下归仁。理所必然也。臣窃闻李珥之死。三医司各司书吏等皆哭奠。发引之日。都中之民。倾都出送。炬火连亘十馀里。此 国朝以来所未有也。以此观之。则其贤德之入人心。非独士类为然。当时民庶皆然也。此岂指嗾而使之。昔司马光之死。民间皆设像而祭之。至于靖康之乱。司马光家属避向南方。中路为群盗所掠。至于其酋长处。其酋迎之坐而语之曰。司马相公家属。吾何敢犯。其所虏人口财产。皆收聚而归之。又使其卒护送。然则善之感人。虽盗贼亦然也。唯其时蔡京,章惇等得志之徒深疾之。至立碑而锢之。人之不仁。其至此夫。今此两臣之贤。敬慕之心。殆至举国同然。而独柳㮨辈若干人。极力构陷。其亦不仁甚矣。岭北之地。虽文学不足。素称陋邦。秉彝之性。人所均禀。而两臣德义声名。无远不及。此儒生等虽不能深知贤者之事。亦何独不得闻其风乎。自以名在儒籍。尊贤之诚。何独后于他道。乃相率远来耳。 圣意乃疑其为指嗾而来。窃恐其未必然也。夫两臣尊慕之论。乃举世之公言也。何至借力于遐方疲残之儒哉。其言又岂有轻重哉。且千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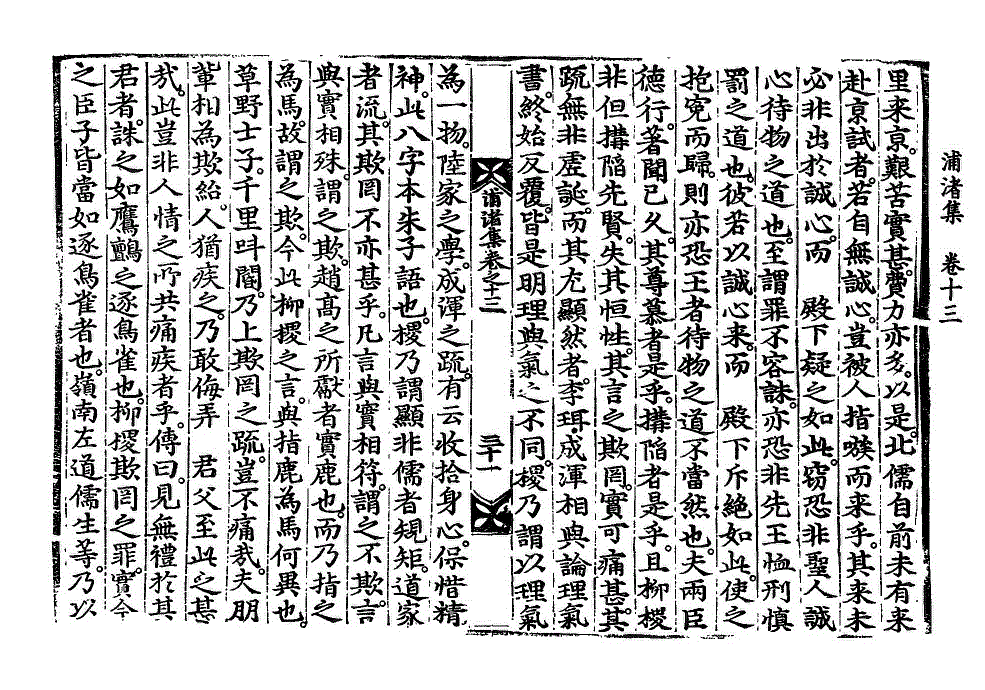 里来京。艰苦实甚。费力亦多。以是。北儒自前未有来赴京试者。若自无诚心。岂被人指嗾而来乎。其来未必非出于诚心。而 殿下疑之如此。窃恐非圣人诚心待物之道也。至谓罪不容诛。亦恐非先王恤刑慎罚之道也。彼若以诚心来。而 殿下斥绝如此。使之抱冤而归。则亦恐王者待物之道不当然也。夫两臣德行。著闻已久。其尊慕者是乎。搆陷者是乎。且柳㮨非但搆陷先贤。失其恒性。其言之欺罔。实可痛甚。其疏无非虚诞。而其尤显然者。李珥,成浑相与论理气书。终始反覆。皆是明理与气之不同。㮨乃谓以理气为一物。陆家之学。成浑之疏。有云收拾身心。保惜精神。此八字本朱子语也。㮨乃谓显非儒者规矩。道家者流。其欺罔不亦甚乎。凡言与实相符。谓之不欺。言与实相殊。谓之欺。赵高之所献者实鹿也。而乃指之为马。故谓之欺。今此柳㮨之言。与指鹿为马何异也。草野士子。千里叫阍。乃上欺罔之疏。岂不痛哉。夫朋辈相为欺绐。人犹疾之。乃敢侮弄 君父至此之甚哉。此岂非人情之所共痛疾者乎。传曰。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柳㮨欺罔之罪。实今之臣子皆当如逐鸟雀者也。岭南左道儒生等。乃以
里来京。艰苦实甚。费力亦多。以是。北儒自前未有来赴京试者。若自无诚心。岂被人指嗾而来乎。其来未必非出于诚心。而 殿下疑之如此。窃恐非圣人诚心待物之道也。至谓罪不容诛。亦恐非先王恤刑慎罚之道也。彼若以诚心来。而 殿下斥绝如此。使之抱冤而归。则亦恐王者待物之道不当然也。夫两臣德行。著闻已久。其尊慕者是乎。搆陷者是乎。且柳㮨非但搆陷先贤。失其恒性。其言之欺罔。实可痛甚。其疏无非虚诞。而其尤显然者。李珥,成浑相与论理气书。终始反覆。皆是明理与气之不同。㮨乃谓以理气为一物。陆家之学。成浑之疏。有云收拾身心。保惜精神。此八字本朱子语也。㮨乃谓显非儒者规矩。道家者流。其欺罔不亦甚乎。凡言与实相符。谓之不欺。言与实相殊。谓之欺。赵高之所献者实鹿也。而乃指之为马。故谓之欺。今此柳㮨之言。与指鹿为马何异也。草野士子。千里叫阍。乃上欺罔之疏。岂不痛哉。夫朋辈相为欺绐。人犹疾之。乃敢侮弄 君父至此之甚哉。此岂非人情之所共痛疾者乎。传曰。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柳㮨欺罔之罪。实今之臣子皆当如逐鸟雀者也。岭南左道儒生等。乃以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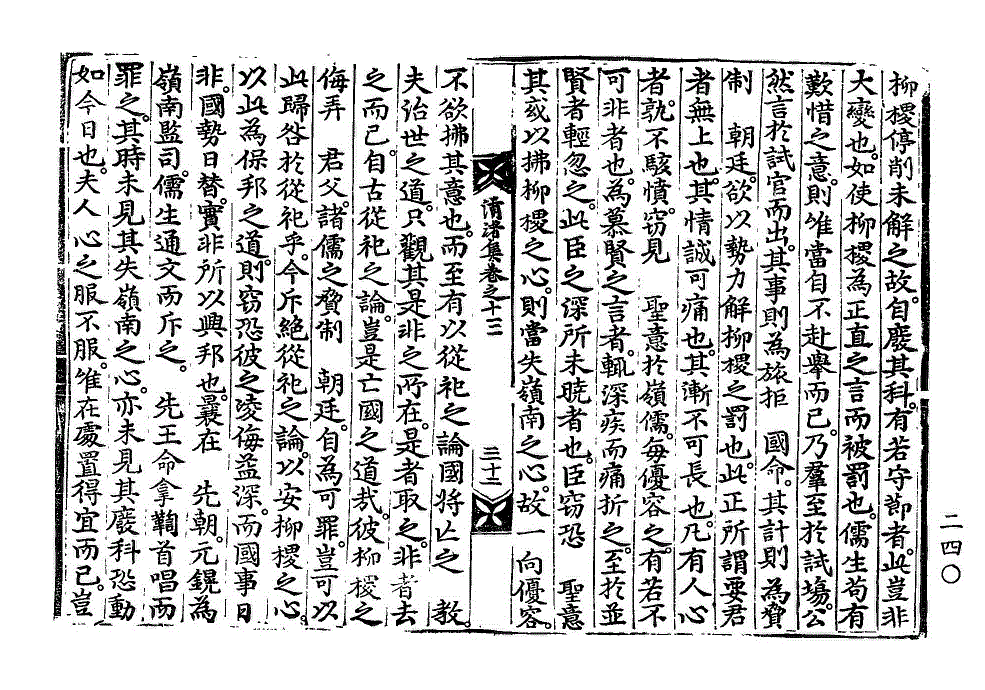 柳㮨停削未解之故。自废其科。有若守节者。此岂非大变也。如使柳㮨为正直之言而被罚也。儒生苟有叹惜之意。则唯当自不赴举而已。乃群至于试场。公然言于试官而出。其事则为旅拒 国命。其计则为胁制 朝廷。欲以势力解柳㮨之罚也。此正所谓要君者无上也。其情诚可痛也。其渐不可长也。凡有人心者。孰不骇愤。窃见 圣意于岭儒。每优容之。有若不可非者也。为慕贤之言者。辄深疾而痛折之。至于并贤者轻忽之。此臣之深所未晓者也。臣窃恐 圣意其或以拂柳㮨之心。则当失岭南之心。故一向优容。不欲拂其意也。而至有以从祀之论国将亡之 教。夫治世之道。只观其是非之所在。是者取之。非者去之而已。自古从祀之论。岂是亡国之道哉。彼柳㮨之侮弄 君父。诸儒之胁制 朝廷。自为可罪。岂可以此归咎于从祀乎。今斥绝从祀之论。以安柳㮨之心。以此为保邦之道。则窃恐彼之凌侮益深。而国事日非。国势日替。实非所以兴邦也。曩在 先朝。元鎤为岭南监司。儒生通文而斥之。 先王命拿鞫首唱而罪之。其时未见其失岭南之心。亦未见其废科恐动如今日也。夫人心之服不服。唯在处置得宜而已。岂
柳㮨停削未解之故。自废其科。有若守节者。此岂非大变也。如使柳㮨为正直之言而被罚也。儒生苟有叹惜之意。则唯当自不赴举而已。乃群至于试场。公然言于试官而出。其事则为旅拒 国命。其计则为胁制 朝廷。欲以势力解柳㮨之罚也。此正所谓要君者无上也。其情诚可痛也。其渐不可长也。凡有人心者。孰不骇愤。窃见 圣意于岭儒。每优容之。有若不可非者也。为慕贤之言者。辄深疾而痛折之。至于并贤者轻忽之。此臣之深所未晓者也。臣窃恐 圣意其或以拂柳㮨之心。则当失岭南之心。故一向优容。不欲拂其意也。而至有以从祀之论国将亡之 教。夫治世之道。只观其是非之所在。是者取之。非者去之而已。自古从祀之论。岂是亡国之道哉。彼柳㮨之侮弄 君父。诸儒之胁制 朝廷。自为可罪。岂可以此归咎于从祀乎。今斥绝从祀之论。以安柳㮨之心。以此为保邦之道。则窃恐彼之凌侮益深。而国事日非。国势日替。实非所以兴邦也。曩在 先朝。元鎤为岭南监司。儒生通文而斥之。 先王命拿鞫首唱而罪之。其时未见其失岭南之心。亦未见其废科恐动如今日也。夫人心之服不服。唯在处置得宜而已。岂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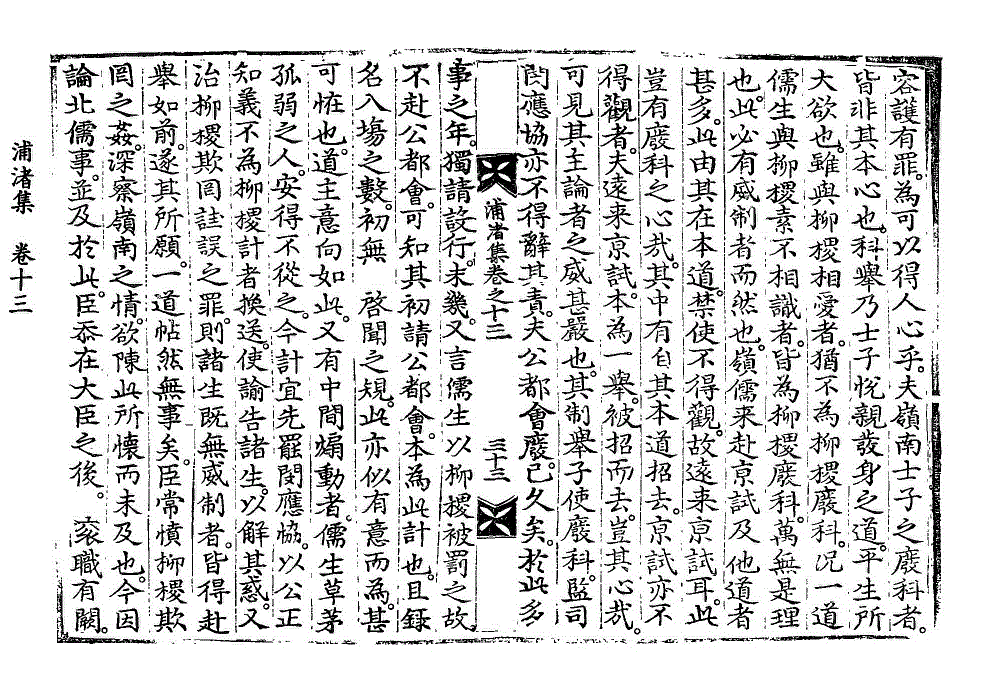 容护有罪。为可以得人心乎。夫岭南士子之废科者。皆非其本心也。科举乃士子悦亲发身之道。平生所大欲也。虽与柳㮨相爱者。犹不为柳㮨废科。况一道儒生与柳㮨素不相识者。皆为柳㮨废科。万无是理也。此必有威制者而然也。岭儒来赴京试及他道者甚多。此由其在本道。禁使不得观。故远来京试耳。此岂有废科之心哉。其中有自其本道招去。京试亦不得观者。夫远来京试。本为一举。被招而去。岂其心哉。可见其主论者之威甚严也。其制举子使废科。监司闵应协亦不得辞其责。夫公都会废。已久矣。于此多事之年。独请设行。未几。又言儒生以柳㮨被罚之故。不赴公都会。可知其初请公都会。本为此计也。且录名入场之数。初无 启闻之规。此亦似有意而为。甚可怪也。道主意向如此。又有中间煽动者。儒生草茅孤弱之人。安得不从之。今计宜先罢闵应协。以公正知义不为柳㮨计者换送。使谕告诸生。以解其惑。又治柳㮨欺罔诖误之罪。则诸生既无威制者。皆得赴举如前。遂其所愿。一道帖然无事矣。臣常愤柳㮨欺罔之奸。深察岭南之情。欲陈此所怀而未及也。今因论北儒事。并及于此。臣忝在大臣之后。 衮职有阙。
容护有罪。为可以得人心乎。夫岭南士子之废科者。皆非其本心也。科举乃士子悦亲发身之道。平生所大欲也。虽与柳㮨相爱者。犹不为柳㮨废科。况一道儒生与柳㮨素不相识者。皆为柳㮨废科。万无是理也。此必有威制者而然也。岭儒来赴京试及他道者甚多。此由其在本道。禁使不得观。故远来京试耳。此岂有废科之心哉。其中有自其本道招去。京试亦不得观者。夫远来京试。本为一举。被招而去。岂其心哉。可见其主论者之威甚严也。其制举子使废科。监司闵应协亦不得辞其责。夫公都会废。已久矣。于此多事之年。独请设行。未几。又言儒生以柳㮨被罚之故。不赴公都会。可知其初请公都会。本为此计也。且录名入场之数。初无 启闻之规。此亦似有意而为。甚可怪也。道主意向如此。又有中间煽动者。儒生草茅孤弱之人。安得不从之。今计宜先罢闵应协。以公正知义不为柳㮨计者换送。使谕告诸生。以解其惑。又治柳㮨欺罔诖误之罪。则诸生既无威制者。皆得赴举如前。遂其所愿。一道帖然无事矣。臣常愤柳㮨欺罔之奸。深察岭南之情。欲陈此所怀而未及也。今因论北儒事。并及于此。臣忝在大臣之后。 衮职有阙。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三 第 2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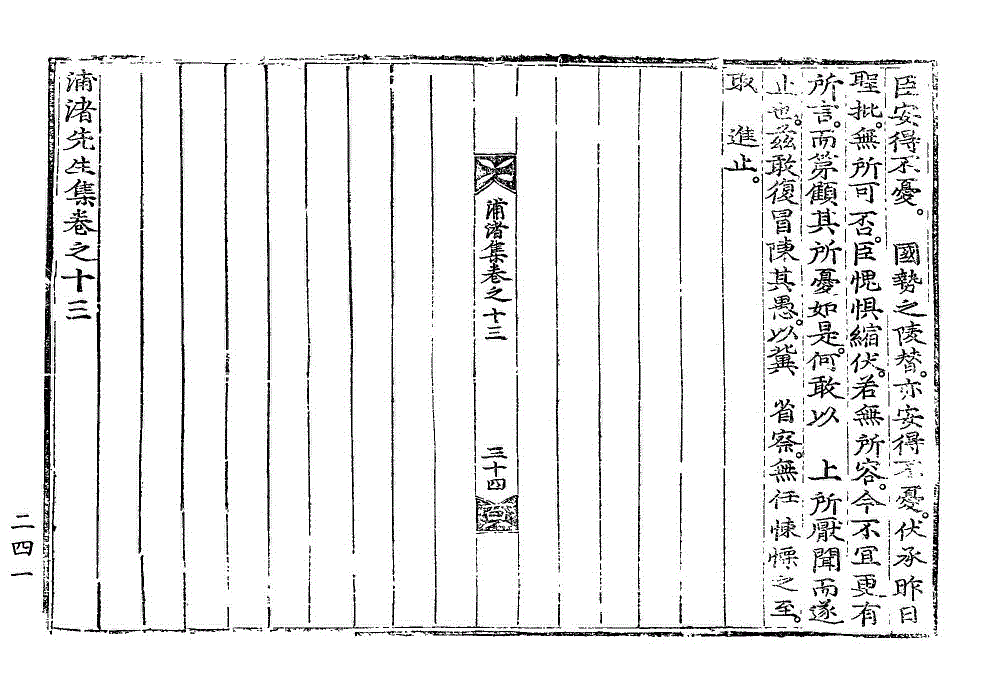 臣安得不忧。 国势之陵替。亦安得不忧。伏承昨日圣批。无所可否。臣愧惧缩伏。若无所容。今不宜更有所言。而第顾其所忧如是。何敢以 上所厌闻而遂止也。玆敢复冒陈其愚。以冀 省察。无任悚慄之至。取 进止。
臣安得不忧。 国势之陵替。亦安得不忧。伏承昨日圣批。无所可否。臣愧惧缩伏。若无所容。今不宜更有所言。而第顾其所忧如是。何敢以 上所厌闻而遂止也。玆敢复冒陈其愚。以冀 省察。无任悚慄之至。取 进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