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x 页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劄(十一首)
劄(十一首)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09H 页
 论 山陵劄(己丑)
论 山陵劄(己丑)伏以 大行大王圣德临御。二十有七年。其恭俭之德。仁爱之诚。终始如一日。浃人心髓。久矣。今者无禄。遽遭 宾天之痛。举国臣民。遑遑号呼。若失所怙。其哀慕之情。曷有其已。窃念此后臣子所以致忠于 大行大王者。唯其尽心于 山陵窀穸之奉。使无未尽之憾而已。地理之说。始于汉,晋间术士。而盛于唐,宋。世间祸福。虽未知必由于地理。而其说流来已久。若皆虚伪。岂能使人崇信如是乎。程子虽不信地理。然有彼安则此安。彼危则此危之说。又云。须取山回水曲。襟抱无亏欠。地家所谓吉地者。亦取如此也。至于朱子。则实深究其说。其葬亲之地。既以其法求之。而又论奏山陵得失甚详。今撮其大略而言之。有曰。以子孙而藏其祖考之遗体。必致其谨重诚敬之心。以为安固久远之计。使其形体全而神灵得安。则其子孙盛而祭祀不绝。此自然之理也。又曰。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无不广招术士。博访名山。参互比较。择其善之尤者。然后用之。其或择之不精。地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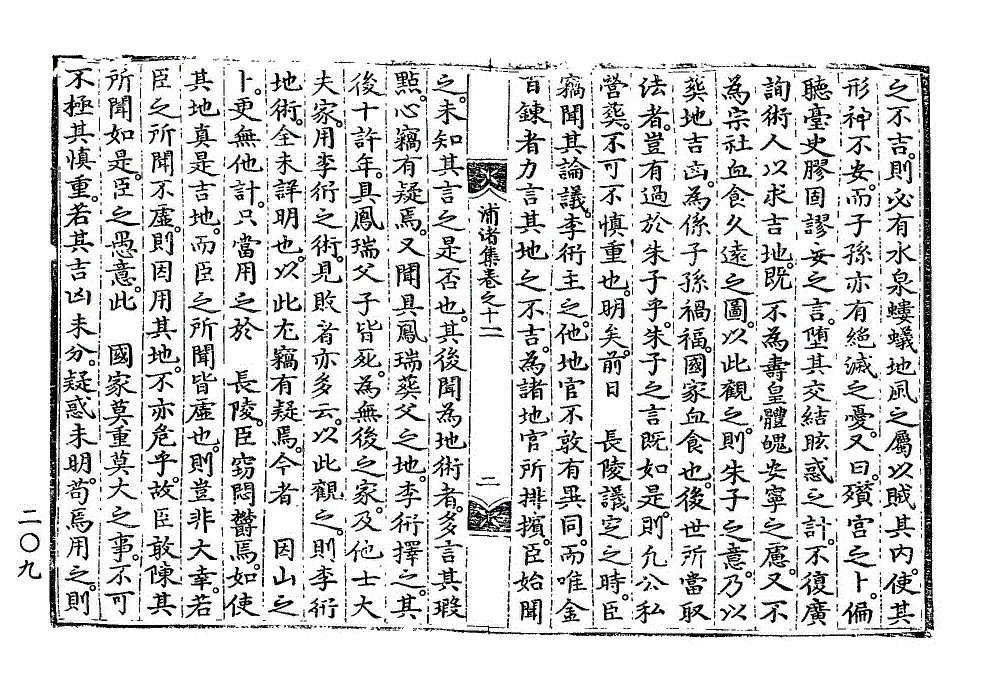 之不吉。则必有水泉蝼蚁地风之属以贼其内。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孙亦有绝灭之忧。又曰。攒宫之卜。偏听台史胶固谬妄之言。堕其交结眩惑之计。不复广询术人以求吉地。既不为寿皇体魄安宁之虑。又不为宗社血食久远之图。以此观之。则朱子之意。乃以葬地吉凶。为系子孙祸福。国家血食也。后世所当取法者。岂有过于朱子乎。朱子之言既如是。则凡公私营葬。不可不慎重也。明矣。前日 长陵议定之时。臣窃闻其论议。李衎主之。他地官不敢有异同。而唯金百鍊者力言其地之不吉。为诸地官所排摈。臣始闻之。未知其言之是否也。其后闻为地术者。多言其瑕点。心窃有疑焉。又闻具凤瑞葬父之地。李衎择之。其后十许年。具凤瑞父子皆死。为无后之家。及他士大夫家。用李衎之术。见败者亦多云。以此观之。则李衎地术。全未详明也。以此尤窃有疑焉。今者 因山之卜。更无他计。只当用之于 长陵。臣窃闷郁焉。如使其地真是吉地。而臣之所闻皆虚也。则岂非大幸。若臣之所闻不虚。则因用其地。不亦危乎。故臣敢陈其所闻如是。臣之愚意。此 国家莫重莫大之事。不可不极其慎重。若其吉凶未分。疑惑未明。苟焉用之。则
之不吉。则必有水泉蝼蚁地风之属以贼其内。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孙亦有绝灭之忧。又曰。攒宫之卜。偏听台史胶固谬妄之言。堕其交结眩惑之计。不复广询术人以求吉地。既不为寿皇体魄安宁之虑。又不为宗社血食久远之图。以此观之。则朱子之意。乃以葬地吉凶。为系子孙祸福。国家血食也。后世所当取法者。岂有过于朱子乎。朱子之言既如是。则凡公私营葬。不可不慎重也。明矣。前日 长陵议定之时。臣窃闻其论议。李衎主之。他地官不敢有异同。而唯金百鍊者力言其地之不吉。为诸地官所排摈。臣始闻之。未知其言之是否也。其后闻为地术者。多言其瑕点。心窃有疑焉。又闻具凤瑞葬父之地。李衎择之。其后十许年。具凤瑞父子皆死。为无后之家。及他士大夫家。用李衎之术。见败者亦多云。以此观之。则李衎地术。全未详明也。以此尤窃有疑焉。今者 因山之卜。更无他计。只当用之于 长陵。臣窃闷郁焉。如使其地真是吉地。而臣之所闻皆虚也。则岂非大幸。若臣之所闻不虚。则因用其地。不亦危乎。故臣敢陈其所闻如是。臣之愚意。此 国家莫重莫大之事。不可不极其慎重。若其吉凶未分。疑惑未明。苟焉用之。则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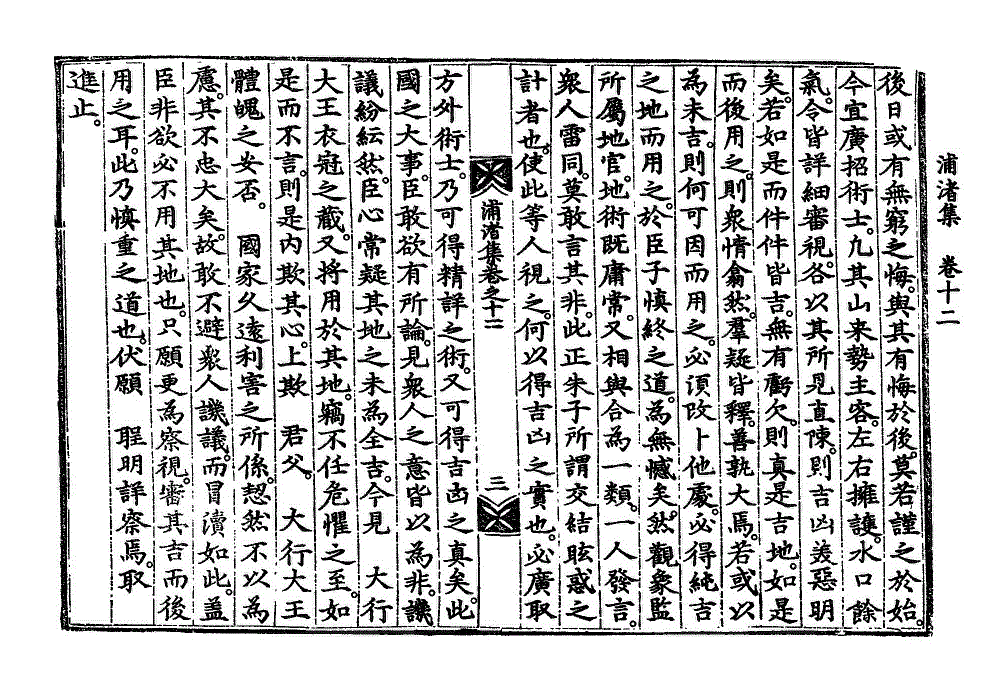 后日或有无穷之悔。与其有悔于后。莫若谨之于始。今宜广招术士。凡其山来势主客。左右拥护。水口馀气。令皆详细审视。各以其所见直陈。则吉凶美恶明矣。若如是而件件皆吉。无有亏欠。则真是吉地。如是而后用之。则众情翕然。群疑皆释。善孰大焉。若或以为未吉。则何可因而用之。必须改卜他处。必得纯吉之地而用之。于臣子慎终之道。为无憾矣。然观象监所属地官。地术既庸常。又相与合为一类。一人发言。众人雷同。莫敢言其非。此正朱子所谓交结眩惑之计者也。使此等人视之。何以得吉凶之实也。必广取方外术士。乃可得精详之术。又可得吉凶之真矣。此国之大事。臣敢欲有所论。见众人之意皆以为非。讥议纷纭然。臣心常疑其地之未为全吉。今见 大行大王衣冠之藏。又将用于其地。窃不任危惧之至。如是而不言。则是内欺其心。上欺 君父。 大行大王体魄之安否。 国家久远利害之所系。恝然不以为虑。其不忠大矣。故敢不避众人讥议。而冒渎如此。盖臣非欲必不用其地也。只愿更为察视。审其吉而后用之耳。此乃慎重之道也。伏愿 圣明详察焉。取 进止。
后日或有无穷之悔。与其有悔于后。莫若谨之于始。今宜广招术士。凡其山来势主客。左右拥护。水口馀气。令皆详细审视。各以其所见直陈。则吉凶美恶明矣。若如是而件件皆吉。无有亏欠。则真是吉地。如是而后用之。则众情翕然。群疑皆释。善孰大焉。若或以为未吉。则何可因而用之。必须改卜他处。必得纯吉之地而用之。于臣子慎终之道。为无憾矣。然观象监所属地官。地术既庸常。又相与合为一类。一人发言。众人雷同。莫敢言其非。此正朱子所谓交结眩惑之计者也。使此等人视之。何以得吉凶之实也。必广取方外术士。乃可得精详之术。又可得吉凶之真矣。此国之大事。臣敢欲有所论。见众人之意皆以为非。讥议纷纭然。臣心常疑其地之未为全吉。今见 大行大王衣冠之藏。又将用于其地。窃不任危惧之至。如是而不言。则是内欺其心。上欺 君父。 大行大王体魄之安否。 国家久远利害之所系。恝然不以为虑。其不忠大矣。故敢不避众人讥议。而冒渎如此。盖臣非欲必不用其地也。只愿更为察视。审其吉而后用之耳。此乃慎重之道也。伏愿 圣明详察焉。取 进止。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10L 页
 辞大司宪劄
辞大司宪劄伏以此时乞递。岂情分所敢。廉耻所关。不得不然。 圣批谆谆。不以为罪。至以匡辅不逮为 教。臣感激悚慄。不能自定。窃念臣知道不明。不能不惑于地术。过听流言。窃用深忧于 国事。适当 因山之卜。妄陈私臆之虑。察其心。虽出于忧国之微诚。论其事。实是为轻妄而可罪。此众人之所以非笑而诋斥之也。非但妄忧众人所不忧。自宜见怪于人也。亦可见素行无可取。不能取信于人也。谤讟若此。何敢自安。冒陈哀恳。实非得已。不谓 天鉴孔昭。下烛微忠。不罪妄言。反 下温旨。区区感激。糜粉难报。至于匡辅之教。实非如臣迂愚朴拙所敢承当。唯有惶恐悚惕措躬无地而已。 恩私至此。臣唯当奔走供职。不敢更辞。而第台官之长。与群僚不同。进退举措。所关甚重。谤议纷兴。晏然仍冒。无耻大矣。虽感 圣眷。人将谓何。反覆思量。决不可冒居。当此 谅闇之日。渎扰至再。罪合万殒。伏乞 圣明察臣情势。 亟命镌改臣职。以谢人言。以重台官进退之节。不胜幸甚。取 进止。
请停 陵幸劄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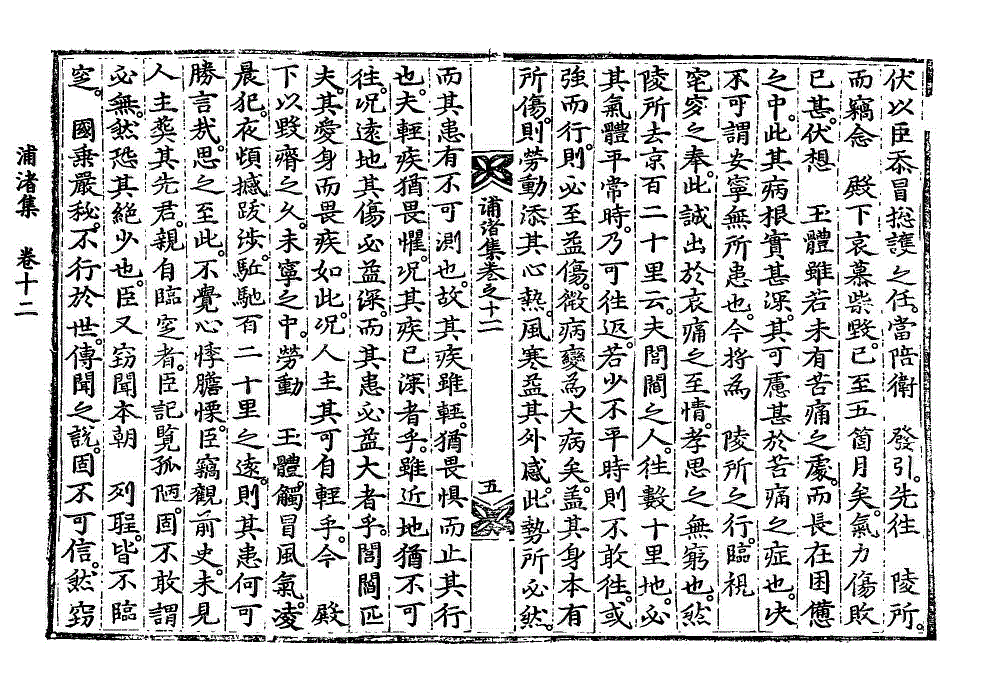 伏以臣忝冒总护之任。当陪卫 发引。先往 陵所。而窃念 殿下哀慕柴毁。已至五个月矣。气力伤败已甚。伏想 玉体虽若未有苦痛之处。而长在困惫之中。此其病根实甚深。其可虑甚于苦痛之症也。决不可谓安宁无所患也。今将为 陵所之行。临视 窀穸之奉。此诚出于哀痛之至情。孝思之无穷也。然陵所去京百二十里云。夫闾阎之人。往数十里地。必其气体平常时。乃可往返。若少不平时则不敢往。或强而行。则必至益伤。微病变为大病矣。盖其身本有所伤。则劳动添其心热。风寒益其外感。此势所必然。而其患有不可测也。故其疾虽轻。犹畏惧而止其行也。夫轻疾犹畏惧。况其疾已深者乎。虽近地犹不可往。况远地其伤必益深。而其患必益大者乎。闾阎匹夫。其爱身而畏疾如此。况人主其可自轻乎。今 殿下以毁瘠之久。未宁之中。劳动 玉体。触冒风气。凌晨犯。夜顿撼跋涉。驱驰百二十里之远。则其患何可胜言哉。思之至此。不觉心悸胆慄。臣窃观前史。未见人主葬其先君。亲自临窆者。臣记览孤陋。固不敢谓必无。然恐其绝少也。臣又窃闻本朝 列圣。皆不临窆。 国乘严秘。不行于世。传闻之说。固不可信。然窃
伏以臣忝冒总护之任。当陪卫 发引。先往 陵所。而窃念 殿下哀慕柴毁。已至五个月矣。气力伤败已甚。伏想 玉体虽若未有苦痛之处。而长在困惫之中。此其病根实甚深。其可虑甚于苦痛之症也。决不可谓安宁无所患也。今将为 陵所之行。临视 窀穸之奉。此诚出于哀痛之至情。孝思之无穷也。然陵所去京百二十里云。夫闾阎之人。往数十里地。必其气体平常时。乃可往返。若少不平时则不敢往。或强而行。则必至益伤。微病变为大病矣。盖其身本有所伤。则劳动添其心热。风寒益其外感。此势所必然。而其患有不可测也。故其疾虽轻。犹畏惧而止其行也。夫轻疾犹畏惧。况其疾已深者乎。虽近地犹不可往。况远地其伤必益深。而其患必益大者乎。闾阎匹夫。其爱身而畏疾如此。况人主其可自轻乎。今 殿下以毁瘠之久。未宁之中。劳动 玉体。触冒风气。凌晨犯。夜顿撼跋涉。驱驰百二十里之远。则其患何可胜言哉。思之至此。不觉心悸胆慄。臣窃观前史。未见人主葬其先君。亲自临窆者。臣记览孤陋。固不敢谓必无。然恐其绝少也。臣又窃闻本朝 列圣。皆不临窆。 国乘严秘。不行于世。传闻之说。固不可信。然窃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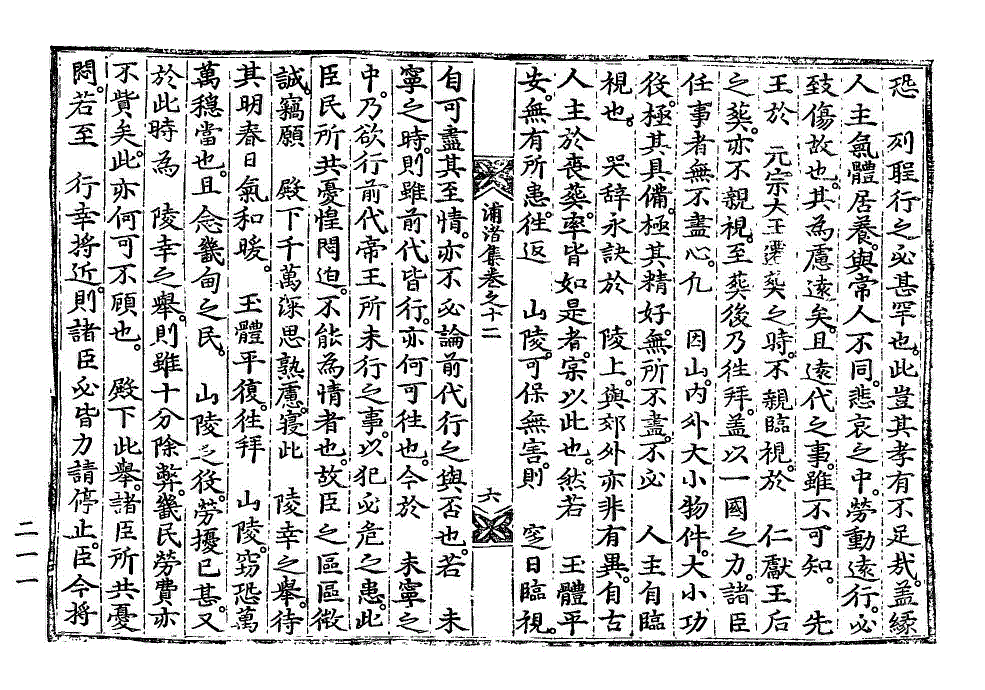 恐 列圣行之必甚罕也。此岂其孝有不足哉。盖缘人主气体居养。与常人不同。悲哀之中。劳动远行。必致伤故也。其为虑远矣。且远代之事。虽不可知。 先王于 元宗大王迁葬之时。不亲临视。于 仁献王后之葬。亦不亲视。至葬后乃往拜。盖以一国之力。诸臣任事者无不尽心。凡 因山。内外大小物件。大小功役。极其具备。极其精好。无所不尽。不必 人主自临视也。 哭辞永诀于 陵上。与郊外亦非有异。自古人主于丧葬。率皆如是者。实以此也。然若 玉体平安。无有所患。往返 山陵。可保无害。则 窆日临视。自可尽其至情。亦不必论前代行之与否也。若 未宁之时。则虽前代皆行。亦何可往也。今于 未宁之中。乃欲行前代帝王所未行之事。以犯必危之患。此臣民所共忧惶闷迫。不能为情者也。故臣之区区微诚。窃愿 殿下千万深思熟虑。寝此 陵幸之举。待其明春日气和暖。 玉体平复。往拜 山陵。窃恐万万稳当也。且念畿甸之民。 山陵之役。劳扰已甚。又于此时为 陵幸之举。则虽十分除弊。畿民劳费亦不赀矣。此亦何可不顾也。 殿下此举。诸臣所共忧闷。若至 行幸将近。则诸臣必皆力请停止。臣今将
恐 列圣行之必甚罕也。此岂其孝有不足哉。盖缘人主气体居养。与常人不同。悲哀之中。劳动远行。必致伤故也。其为虑远矣。且远代之事。虽不可知。 先王于 元宗大王迁葬之时。不亲临视。于 仁献王后之葬。亦不亲视。至葬后乃往拜。盖以一国之力。诸臣任事者无不尽心。凡 因山。内外大小物件。大小功役。极其具备。极其精好。无所不尽。不必 人主自临视也。 哭辞永诀于 陵上。与郊外亦非有异。自古人主于丧葬。率皆如是者。实以此也。然若 玉体平安。无有所患。往返 山陵。可保无害。则 窆日临视。自可尽其至情。亦不必论前代行之与否也。若 未宁之时。则虽前代皆行。亦何可往也。今于 未宁之中。乃欲行前代帝王所未行之事。以犯必危之患。此臣民所共忧惶闷迫。不能为情者也。故臣之区区微诚。窃愿 殿下千万深思熟虑。寝此 陵幸之举。待其明春日气和暖。 玉体平复。往拜 山陵。窃恐万万稳当也。且念畿甸之民。 山陵之役。劳扰已甚。又于此时为 陵幸之举。则虽十分除弊。畿民劳费亦不赀矣。此亦何可不顾也。 殿下此举。诸臣所共忧闷。若至 行幸将近。则诸臣必皆力请停止。臣今将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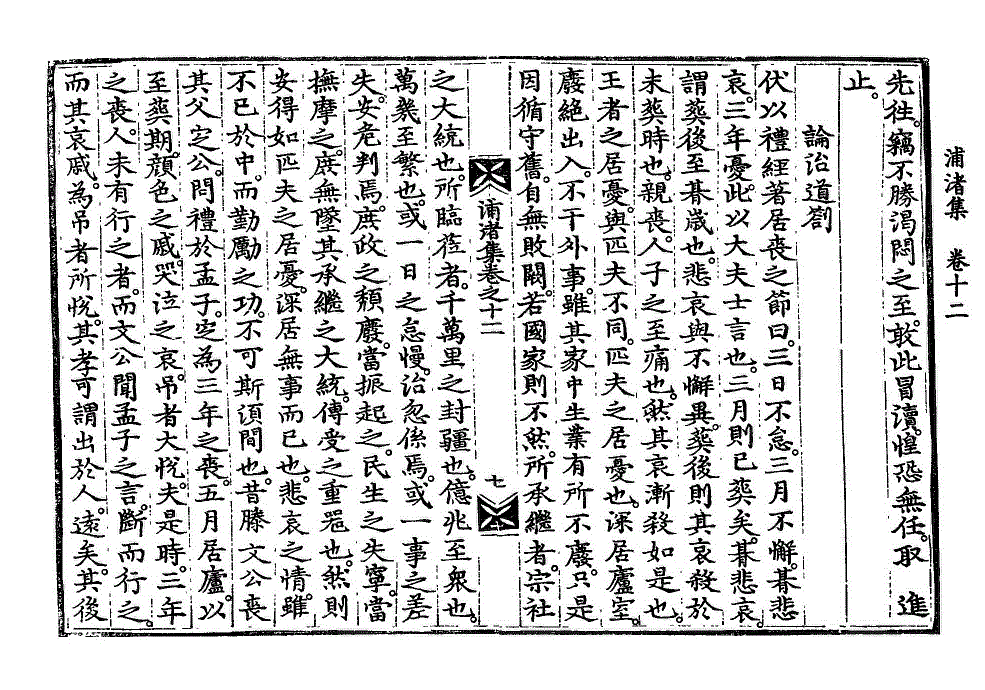 先往。窃不胜渴闷之至。敢此冒渎。惶恐无任。取 进止。
先往。窃不胜渴闷之至。敢此冒渎。惶恐无任。取 进止。论治道劄
伏以礼经著居丧之节曰。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忧。此以大夫士言也。三月则已葬矣。期悲哀。谓葬后至期岁也。悲哀与不懈异。葬后则其哀杀于未葬时也。亲丧。人子之至痛也。然其哀渐杀如是也。王者之居忧。与匹夫不同。匹夫之居忧也。深居庐室。废绝出入。不干外事。虽其家中生业有所不废。只是因循守旧。自无败阙。若国家则不然。所承继者。宗社之大统也。所临莅者。千万里之封疆也。亿兆至众也。万几至繁也。或一日之怠慢。治忽系焉。或一事之差失。安危判焉。庶政之颓废。当振起之。民生之失宁。当抚摩之。庶无坠其承继之大统。传受之重器也。然则安得如匹夫之居忧。深居无事而已也。悲哀之情。虽不已于中。而勤励之功。不可斯须间也。昔滕文公丧其父定公。问礼于孟子。定为三年之丧。五月居庐。以至葬期。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悦。夫是时。三年之丧。人未有行之者。而文公闻孟子之言。断而行之。而其哀戚。为吊者所悦。其孝可谓出于人。远矣。其后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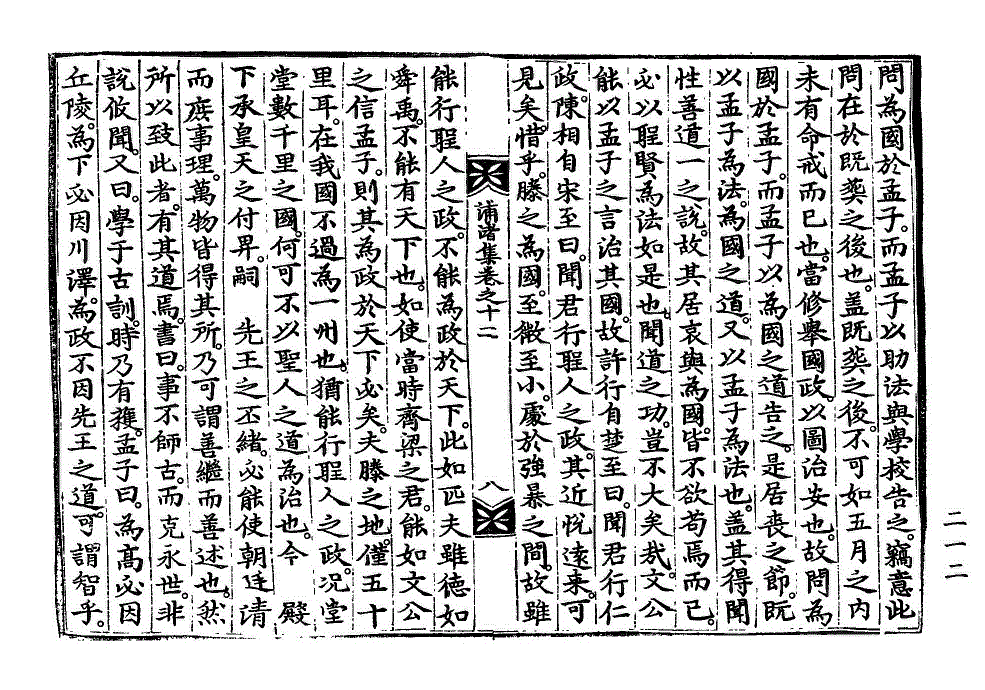 问为国于孟子。而孟子以助法与学校告之。窃意此问在于既葬之后也。盖既葬之后。不可如五月之内未有命戒而已也。当修举国政。以图治安也。故问为国于孟子。而孟子以为国之道告之。是居丧之节。既以孟子为法。为国之道。又以孟子为法也。盖其得闻性善道一之说。故其居哀与为国。皆不欲苟焉而已。必以圣贤为法如是也。闻道之功。岂不大矣哉。文公能以孟子之言治其国。故许行自楚至曰。闻君行仁政。陈相自宋至曰。闻君行圣人之政。其近悦远来。可见矣。惜乎。滕之为国。至微至小。处于强暴之问。故虽能行圣人之政。不能为政于天下。此如匹夫虽德如舜禹。不能有天下也。如使当时齐梁之君。能如文公之信孟子。则其为政于天下必矣。夫滕之地。仅五十里耳。在我国不过为一州也。犹能行圣人之政。况堂堂数千里之国。何可不以圣人之道为治也。今 殿下承皇天之付畀。嗣 先王之丕绪。必能使朝廷清而庶事理。万物皆得其所。乃可谓善继而善述也。然所以致此者。有其道焉。书曰。事不师古。而克永世。非说攸闻。又曰。学于古训。时乃有获。孟子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
问为国于孟子。而孟子以助法与学校告之。窃意此问在于既葬之后也。盖既葬之后。不可如五月之内未有命戒而已也。当修举国政。以图治安也。故问为国于孟子。而孟子以为国之道告之。是居丧之节。既以孟子为法。为国之道。又以孟子为法也。盖其得闻性善道一之说。故其居哀与为国。皆不欲苟焉而已。必以圣贤为法如是也。闻道之功。岂不大矣哉。文公能以孟子之言治其国。故许行自楚至曰。闻君行仁政。陈相自宋至曰。闻君行圣人之政。其近悦远来。可见矣。惜乎。滕之为国。至微至小。处于强暴之问。故虽能行圣人之政。不能为政于天下。此如匹夫虽德如舜禹。不能有天下也。如使当时齐梁之君。能如文公之信孟子。则其为政于天下必矣。夫滕之地。仅五十里耳。在我国不过为一州也。犹能行圣人之政。况堂堂数千里之国。何可不以圣人之道为治也。今 殿下承皇天之付畀。嗣 先王之丕绪。必能使朝廷清而庶事理。万物皆得其所。乃可谓善继而善述也。然所以致此者。有其道焉。书曰。事不师古。而克永世。非说攸闻。又曰。学于古训。时乃有获。孟子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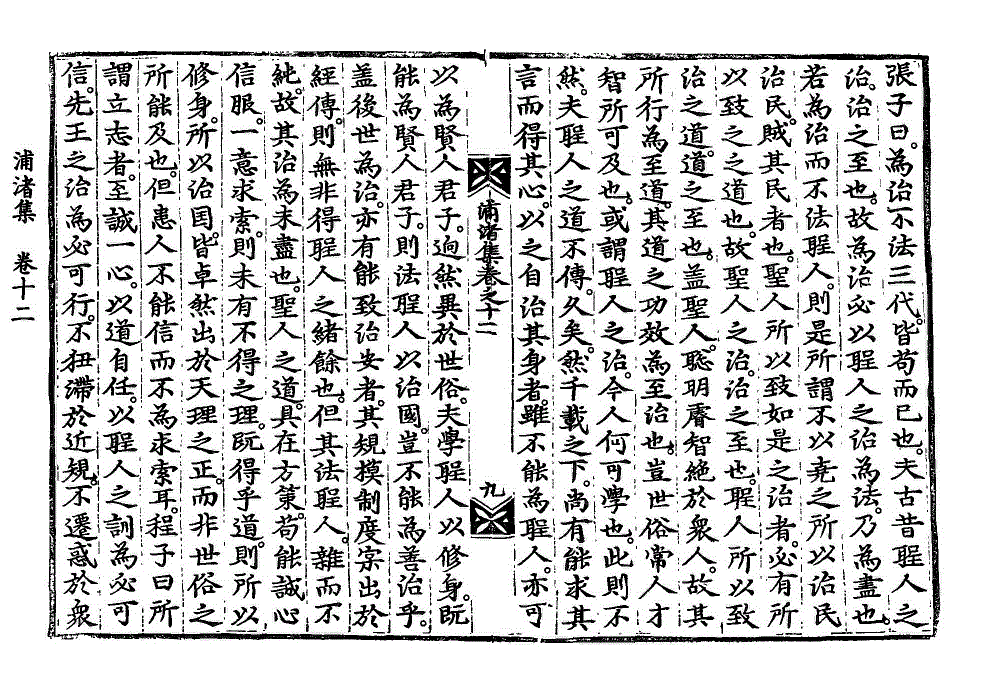 张子曰。为治不法三代。皆苟而已也。夫古昔圣人之治。治之至也。故为治必以圣人之治为法。乃为尽也。若为治而不法圣人。则是所谓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圣人所以致如是之治者。必有所以致之之道也。故圣人之治。治之至也。圣人所以致治之道。道之至也。盖圣人。聪明睿智绝于众人。故其所行为至道。其道之功效为至治也。岂世俗常人才智所可及也。或谓圣人之治。今人何可学也。此则不然。夫圣人之道不传。久矣。然千载之下。尚有能求其言而得其心。以之自治其身者。虽不能为圣人。亦可以为贤人君子。迥然异于世俗。夫学圣人以修身。既能为贤人君子。则法圣人以治国。岂不能为善治乎。盖后世为治。亦有能致治安者。其规模制度实出于经传。则无非得圣人之绪馀也。但其法圣人。杂而不纯。故其治为未尽也。圣人之道。具在方策。苟能诚心信服。一意求索。则未有不得之理。既得乎道。则所以修身。所以治国。皆卓然出于天理之正。而非世俗之所能及也。但患人不能信而不为求索耳。程子曰所谓立志者。至诚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训为必可信。先王之治为必可行。不狃滞于近规。不迁惑于众
张子曰。为治不法三代。皆苟而已也。夫古昔圣人之治。治之至也。故为治必以圣人之治为法。乃为尽也。若为治而不法圣人。则是所谓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圣人所以致如是之治者。必有所以致之之道也。故圣人之治。治之至也。圣人所以致治之道。道之至也。盖圣人。聪明睿智绝于众人。故其所行为至道。其道之功效为至治也。岂世俗常人才智所可及也。或谓圣人之治。今人何可学也。此则不然。夫圣人之道不传。久矣。然千载之下。尚有能求其言而得其心。以之自治其身者。虽不能为圣人。亦可以为贤人君子。迥然异于世俗。夫学圣人以修身。既能为贤人君子。则法圣人以治国。岂不能为善治乎。盖后世为治。亦有能致治安者。其规模制度实出于经传。则无非得圣人之绪馀也。但其法圣人。杂而不纯。故其治为未尽也。圣人之道。具在方策。苟能诚心信服。一意求索。则未有不得之理。既得乎道。则所以修身。所以治国。皆卓然出于天理之正。而非世俗之所能及也。但患人不能信而不为求索耳。程子曰所谓立志者。至诚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训为必可信。先王之治为必可行。不狃滞于近规。不迁惑于众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13L 页
 口。必期治天下如三代之盛也。人主诚能信道如是。则岂有不能致善治之理乎。今者卒哭已过。客使已还。正当留心政务。励精治道。日后治化之盛。实基于今日。而窃恐 殿下信道或未深。立志或未坚。或未能以圣人之治为期也。故敢竭其千虑之愚。进此法圣人之说。窃冀于 圣志之立。有丝毫裨补。此诚区区野人芹曝之忱也。伏愿 圣明怜其愚而察其忱。不胜幸甚。取 进止。
口。必期治天下如三代之盛也。人主诚能信道如是。则岂有不能致善治之理乎。今者卒哭已过。客使已还。正当留心政务。励精治道。日后治化之盛。实基于今日。而窃恐 殿下信道或未深。立志或未坚。或未能以圣人之治为期也。故敢竭其千虑之愚。进此法圣人之说。窃冀于 圣志之立。有丝毫裨补。此诚区区野人芹曝之忱也。伏愿 圣明怜其愚而察其忱。不胜幸甚。取 进止。申论治道。仍进 先朝所献四事劄。
伏以谨按程子曰。治身齐家。以及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纲。分正百职。顺天时以制事。至于创制立度。尽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又曰。治道有从本而言者。有从事而言者。夫程子岂非知治者乎。则此言实为治切要之法也。盖为治之道。有本焉有事焉。如舜之授禹危微精一之言。治之本也。其命四岳九官。分治众职者。治之事也。二者皆为治之大要。不可偏废者也。无其本则人欲肆而天理亡。用舍举措。皆失其正。乱由而生。何以为治乎。无其事则生民之利无以兴。生民之害无以除。其泽不及于民。民生何由而遂。民德何由而正乎。古昔帝王。为治之道不过此两端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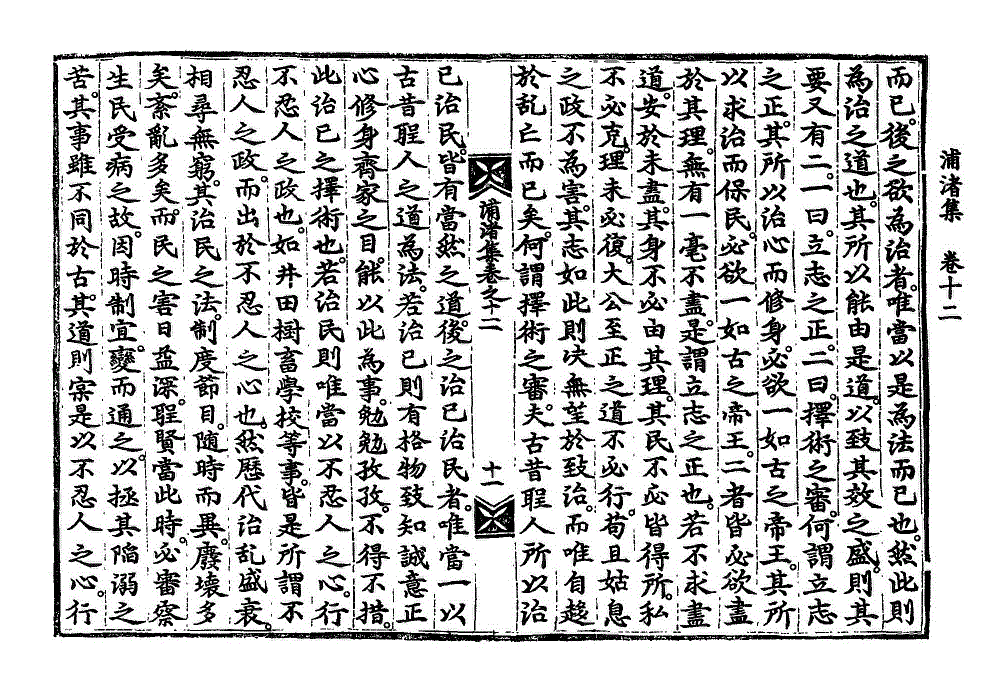 而已。后之欲为治者。唯当以是为法而已也。然此则为治之道也。其所以能由是道。以致其效之盛。则其要又有二。一曰。立志之正。二曰。择术之审。何谓立志之正。其所以治心而修身。必欲一如古之帝王。其所以求治而保民。必欲一如古之帝王。二者皆必欲尽于其理。无有一毫不尽。是谓立志之正也。若不求尽道。安于未尽。其身不必由其理。其民不必皆得所。私不必克。理未必复。大公至正之道不必行。苟且姑息之政不为害。其志如此则决无望于致治。而唯自趋于乱亡而已矣。何谓择术之审。夫古昔圣人所以治己治民。皆有当然之道。后之治己治民者。唯当一以古昔圣人之道为法。若治己则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之目。能以此为事。勉勉孜孜。不得不措。此治己之择术也。若治民则唯当以不忍人之心。行忍人之政也。如井田树畜学校等事。皆是所谓不忍人之政。而出于不忍人之心也。然历代治乱盛衰。相寻无穷。其治民之法。制度节目。随时而异。废坏多矣。紊乱多矣。而民之害日益深。圣贤当此时。必审察生民受病之故。因时制宜。变而通之。以拯其陷溺之苦。其事虽不同于古。其道则实是以不忍人之心。行
而已。后之欲为治者。唯当以是为法而已也。然此则为治之道也。其所以能由是道。以致其效之盛。则其要又有二。一曰。立志之正。二曰。择术之审。何谓立志之正。其所以治心而修身。必欲一如古之帝王。其所以求治而保民。必欲一如古之帝王。二者皆必欲尽于其理。无有一毫不尽。是谓立志之正也。若不求尽道。安于未尽。其身不必由其理。其民不必皆得所。私不必克。理未必复。大公至正之道不必行。苟且姑息之政不为害。其志如此则决无望于致治。而唯自趋于乱亡而已矣。何谓择术之审。夫古昔圣人所以治己治民。皆有当然之道。后之治己治民者。唯当一以古昔圣人之道为法。若治己则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之目。能以此为事。勉勉孜孜。不得不措。此治己之择术也。若治民则唯当以不忍人之心。行忍人之政也。如井田树畜学校等事。皆是所谓不忍人之政。而出于不忍人之心也。然历代治乱盛衰。相寻无穷。其治民之法。制度节目。随时而异。废坏多矣。紊乱多矣。而民之害日益深。圣贤当此时。必审察生民受病之故。因时制宜。变而通之。以拯其陷溺之苦。其事虽不同于古。其道则实是以不忍人之心。行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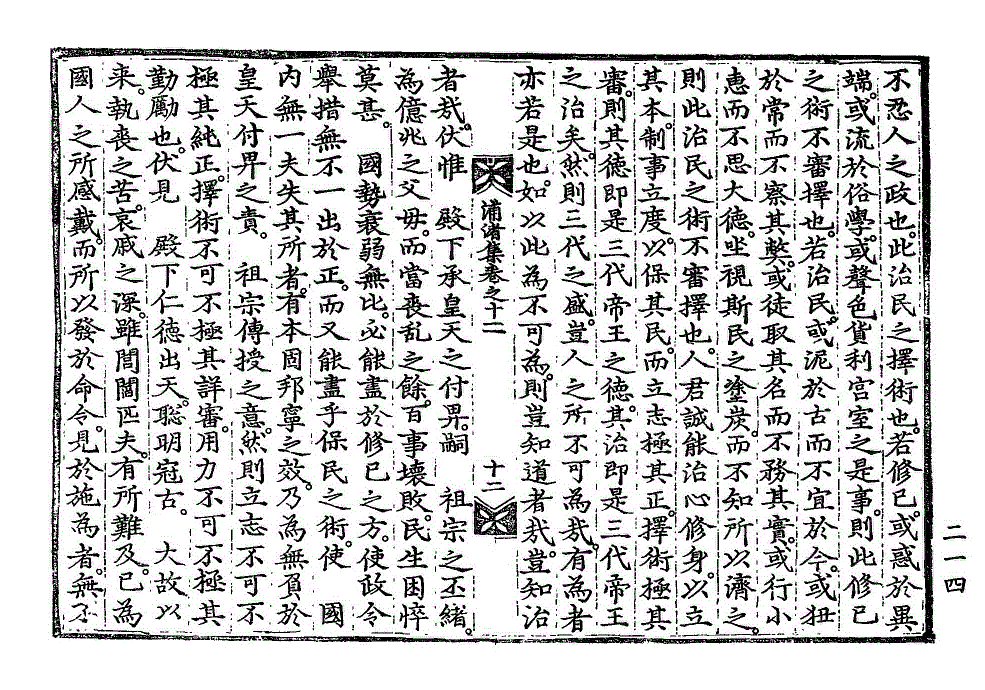 不忍人之政也。此治民之择术也。若修己。或惑于异端。或流于俗学。或声色货利宫室之是事。则此修己之术不审择也。若治民。或泥于古而不宜于今。或狃于常而不察其弊。或徒取其名而不务其实。或行小惠而不思大德。坐视斯民之涂炭。而不知所以济之。则此治民之术不审择也。人君诚能治心修身。以立其本。制事立度。以保其民。而立志极其正。择术极其审。则其德即是三代帝王之德。其治即是三代帝王之治矣。然则三代之盛。岂人之所不可为哉。有为者亦若是也。如以此为不可为。则岂知道者哉。岂知治者哉。伏惟 殿下承皇天之付畀。嗣 祖宗之丕绪。为亿兆之父母。而当丧乱之馀。百事坏败。民生困悴莫甚。 国势衰弱无比。必能尽于修己之方。使政令举措无不一出于正。而又能尽乎保民之术。使 国内无一夫失其所者。有本固邦宁之效。乃为无负于皇天付畀之责。 祖宗传授之意。然则立志不可不极其纯正。择术不可不极其详审。用力不可不极其勤励也。伏见 殿下仁德出天。聪明冠古。 大故以来。执丧之苦。哀戚之深。虽闾阎匹夫。有所难及。已为国人之所感戴。而所以发于命令。见于施为者。无不
不忍人之政也。此治民之择术也。若修己。或惑于异端。或流于俗学。或声色货利宫室之是事。则此修己之术不审择也。若治民。或泥于古而不宜于今。或狃于常而不察其弊。或徒取其名而不务其实。或行小惠而不思大德。坐视斯民之涂炭。而不知所以济之。则此治民之术不审择也。人君诚能治心修身。以立其本。制事立度。以保其民。而立志极其正。择术极其审。则其德即是三代帝王之德。其治即是三代帝王之治矣。然则三代之盛。岂人之所不可为哉。有为者亦若是也。如以此为不可为。则岂知道者哉。岂知治者哉。伏惟 殿下承皇天之付畀。嗣 祖宗之丕绪。为亿兆之父母。而当丧乱之馀。百事坏败。民生困悴莫甚。 国势衰弱无比。必能尽于修己之方。使政令举措无不一出于正。而又能尽乎保民之术。使 国内无一夫失其所者。有本固邦宁之效。乃为无负于皇天付畀之责。 祖宗传授之意。然则立志不可不极其纯正。择术不可不极其详审。用力不可不极其勤励也。伏见 殿下仁德出天。聪明冠古。 大故以来。执丧之苦。哀戚之深。虽闾阎匹夫。有所难及。已为国人之所感戴。而所以发于命令。见于施为者。无不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15H 页
 动合人心。国人咸知 殿下有大有为之志。庶几其能振作颓靡。修举弊坏。跻一世于治安之域。皆颙然有望。此可见天意欲平治我东也。若于是而不能大有所为无以副神人之望。岂非千载之大恨也。臣本迂儒。性甚愚拙。自少不得见取于时。而唯幸知读圣贤之书而悦之。因得以究心焉。凡古昔圣人修己治人之方。思之熟矣。而又窃有区区忧世之念。当世之弊病。亦常寻求而忧叹也。 反正之后。滥蒙 先王恩遇。历忝显列凡十有馀年。常不自量度。冒陈胸中所怀者累矣。其时大臣。所见不同。终不得行。常窃叹之。臣之妄言。其一则乃人主进学之方。修德之要也。其三则曰。田役之弊也。曰。军役之苦也。曰。科举背讲之害也。此三者乃臣平生极意思量。而欲变之者也。常窃以为当今安民救世之策。在此三者。而更无他计也。苟能行此。则凡国中流来积弊。一切尽去。弊去而治至。如病去而身安矣。今臣伏蒙 误恩。叨冒至此。辞不获 命。唯积悚惧。第既在其位。则不可徒备员充位而已。唯思竭诚尽瘁。以图报效。而其平生所蕴。唯在此四者而已。昔宋臣司马光在仁宗朝。上劄论仁明武及任官信赏必罚六事。至英宗朝。又论此
动合人心。国人咸知 殿下有大有为之志。庶几其能振作颓靡。修举弊坏。跻一世于治安之域。皆颙然有望。此可见天意欲平治我东也。若于是而不能大有所为无以副神人之望。岂非千载之大恨也。臣本迂儒。性甚愚拙。自少不得见取于时。而唯幸知读圣贤之书而悦之。因得以究心焉。凡古昔圣人修己治人之方。思之熟矣。而又窃有区区忧世之念。当世之弊病。亦常寻求而忧叹也。 反正之后。滥蒙 先王恩遇。历忝显列凡十有馀年。常不自量度。冒陈胸中所怀者累矣。其时大臣。所见不同。终不得行。常窃叹之。臣之妄言。其一则乃人主进学之方。修德之要也。其三则曰。田役之弊也。曰。军役之苦也。曰。科举背讲之害也。此三者乃臣平生极意思量。而欲变之者也。常窃以为当今安民救世之策。在此三者。而更无他计也。苟能行此。则凡国中流来积弊。一切尽去。弊去而治至。如病去而身安矣。今臣伏蒙 误恩。叨冒至此。辞不获 命。唯积悚惧。第既在其位。则不可徒备员充位而已。唯思竭诚尽瘁。以图报效。而其平生所蕴。唯在此四者而已。昔宋臣司马光在仁宗朝。上劄论仁明武及任官信赏必罚六事。至英宗朝。又论此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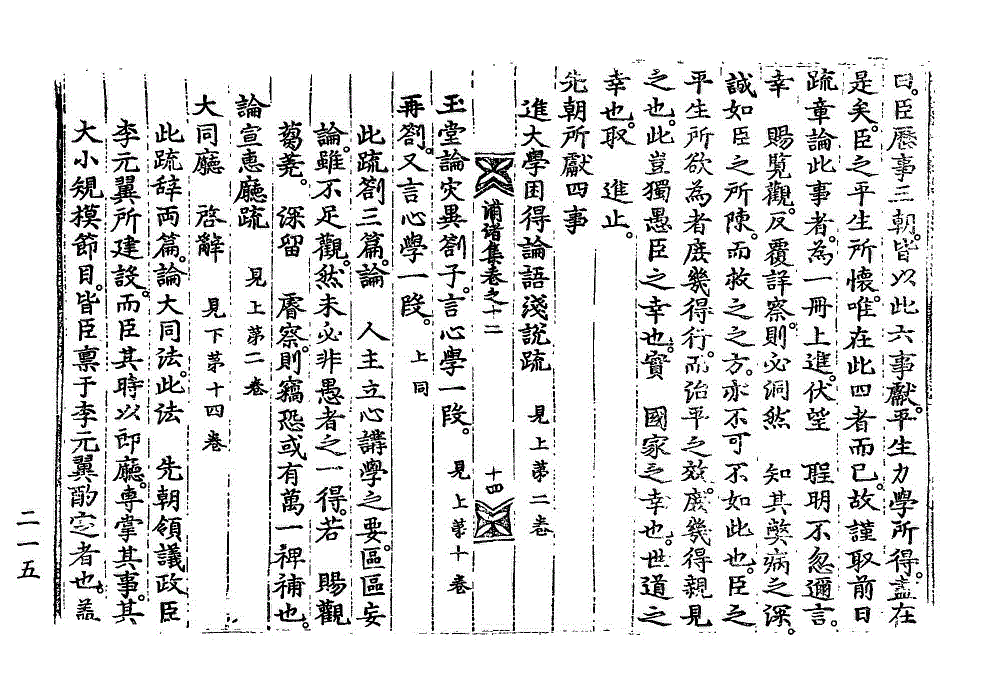 曰。臣历事三朝。皆以此六事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臣之平生所怀。唯在此四者而已。故谨取前日疏章论此事者。为一册上进。伏望 圣明不忽迩言。幸 赐览观。反覆详察。则必洞然 知其弊病之深。诚如臣之所陈。而救之之方。亦不可不如此也。臣之平生所欲为者庶几得行。而治平之效。庶几得亲见之也。此岂独愚臣之幸也。实 国家之幸也。世道之幸也。取 进止。
曰。臣历事三朝。皆以此六事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臣之平生所怀。唯在此四者而已。故谨取前日疏章论此事者。为一册上进。伏望 圣明不忽迩言。幸 赐览观。反覆详察。则必洞然 知其弊病之深。诚如臣之所陈。而救之之方。亦不可不如此也。臣之平生所欲为者庶几得行。而治平之效。庶几得亲见之也。此岂独愚臣之幸也。实 国家之幸也。世道之幸也。取 进止。先朝所献四事
进大学困得论语浅说疏(见上第二卷)
玉堂论灾异劄子。言心学一段。(见上第十卷)
再劄。又言心学一段。(上同)
此疏劄三篇。论 人主立心讲学之要。区区妄论。虽不足观。然未必非愚者之一得。若 赐观刍荛。 深留 睿察。则窃恐或有万一裨补也。
论宣惠厅疏(见上第二卷)
大同厅 启辞(见下第十四卷)
此疏辞两篇。论大同法。此法 先朝领议政臣李元翼所建设。而臣其时以郎厅。专掌其事。其大小规模节目。皆臣禀于李元翼酌定者也。盖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16H 页
 臣既被差郎厅。而窃见其法最为近古。诚是为国之急务。故窃不惮勤劳。日夜思虑计画。得粗成规模。而其时诸臣。不便者多。论议纷纭。臣力主其说。终始不挠。及 先王不免为众说所动。至欲罢之。臣上疏论之。 圣批云。详陈利害。解予疑惑。良用嘉悦。因得不罢。行之一年。京外人情皆悦之。竟以浮议罢。臣窃痛之。 圣明若深察臣之妄说。则有以知此法可以足民。可以足国。而近于古昔王者之政也。当初磨鍊。则依京畿例。以米十六斗为定矣。其后因兵乱饥馑。屡变其制。终未及完定而罢。自今观之。则不必至十六斗而足矣。以孟子百亩之田。五亩之宅。不夺农时。耕者什一等语观之。则此制为赋敛一定之法。实王政之所当先也。令欲保民图治。不可不行此法也。故敢复以此说进。伏愿 圣明垂察焉。
臣既被差郎厅。而窃见其法最为近古。诚是为国之急务。故窃不惮勤劳。日夜思虑计画。得粗成规模。而其时诸臣。不便者多。论议纷纭。臣力主其说。终始不挠。及 先王不免为众说所动。至欲罢之。臣上疏论之。 圣批云。详陈利害。解予疑惑。良用嘉悦。因得不罢。行之一年。京外人情皆悦之。竟以浮议罢。臣窃痛之。 圣明若深察臣之妄说。则有以知此法可以足民。可以足国。而近于古昔王者之政也。当初磨鍊。则依京畿例。以米十六斗为定矣。其后因兵乱饥馑。屡变其制。终未及完定而罢。自今观之。则不必至十六斗而足矣。以孟子百亩之田。五亩之宅。不夺农时。耕者什一等语观之。则此制为赋敛一定之法。实王政之所当先也。令欲保民图治。不可不行此法也。故敢复以此说进。伏愿 圣明垂察焉。丙子劄子。言军政一段。(见上第十一卷)
此一段。论军役之苦。今之为军役者。实皆倒悬之急。极不可忍者也。今此所论。粗举其概。而亦可见其极不可堪之苦也。为国之道。岂可使民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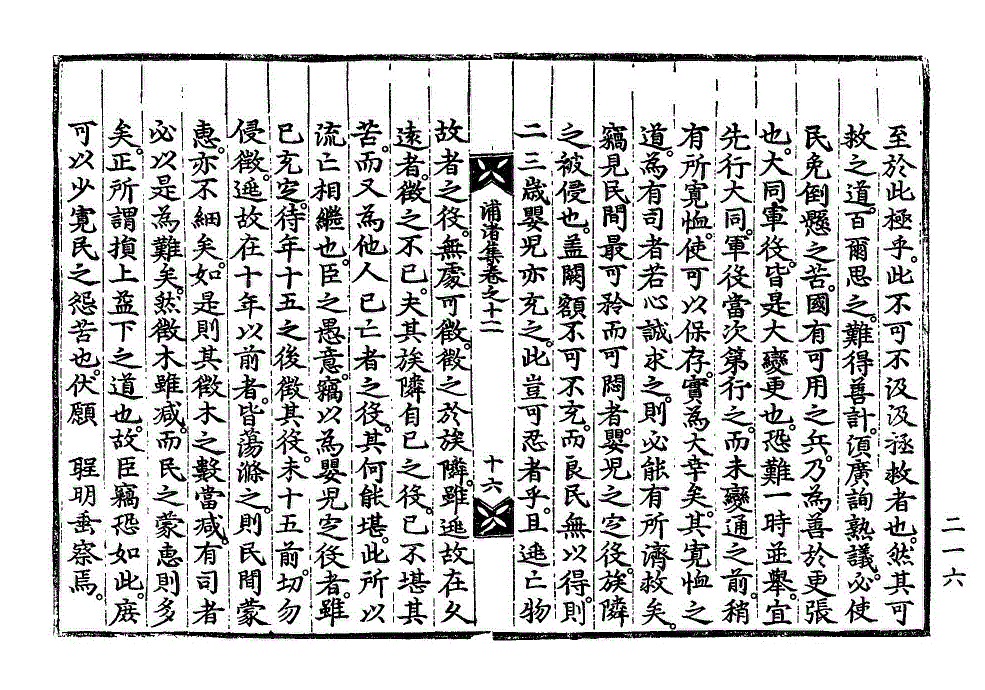 至于此极乎。此不可不汲汲拯救者也。然其可救之道。百尔思之。难得善计。须广询熟议。必使民免倒悬之苦。国有可用之兵。乃为善于更张也。大同,军役。皆是大变更也。恐难一时并举。宜先行大同。军役当次第行之。而未变通之前。稍有所宽恤。使可以保存。实为大幸矣。其宽恤之道。为有司者若心诚求之。则必能有所济救矣。窃见民间最可矜而可闷者。婴儿之定役。族邻之被侵也。盖阙额不可不充。而良民无以得。则二三岁婴儿亦充之。此岂可忍者乎。且逃亡物故者之役。无处可徵。徵之于族邻。虽逃故在久远者。徵之不已。夫其族邻自己之役。已不堪其苦。而又为他人已亡者之役。其何能堪。此所以流亡相继也。臣之愚意。窃以为婴儿定役者。虽已充定。待年十五之后徵其役。未十五前。切勿侵徵。逃故在十年以前者。皆荡涤之。则民间蒙惠。亦不细矣。如是则其徵木之数当减。有司者必以是为难矣。然徵木虽减。而民之蒙惠则多矣。正所谓损上益下之道也。故臣窃恐如此。庶可以少宽民之怨苦也。伏愿 圣明垂察焉。
至于此极乎。此不可不汲汲拯救者也。然其可救之道。百尔思之。难得善计。须广询熟议。必使民免倒悬之苦。国有可用之兵。乃为善于更张也。大同,军役。皆是大变更也。恐难一时并举。宜先行大同。军役当次第行之。而未变通之前。稍有所宽恤。使可以保存。实为大幸矣。其宽恤之道。为有司者若心诚求之。则必能有所济救矣。窃见民间最可矜而可闷者。婴儿之定役。族邻之被侵也。盖阙额不可不充。而良民无以得。则二三岁婴儿亦充之。此岂可忍者乎。且逃亡物故者之役。无处可徵。徵之于族邻。虽逃故在久远者。徵之不已。夫其族邻自己之役。已不堪其苦。而又为他人已亡者之役。其何能堪。此所以流亡相继也。臣之愚意。窃以为婴儿定役者。虽已充定。待年十五之后徵其役。未十五前。切勿侵徵。逃故在十年以前者。皆荡涤之。则民间蒙惠。亦不细矣。如是则其徵木之数当减。有司者必以是为难矣。然徵木虽减。而民之蒙惠则多矣。正所谓损上益下之道也。故臣窃恐如此。庶可以少宽民之怨苦也。伏愿 圣明垂察焉。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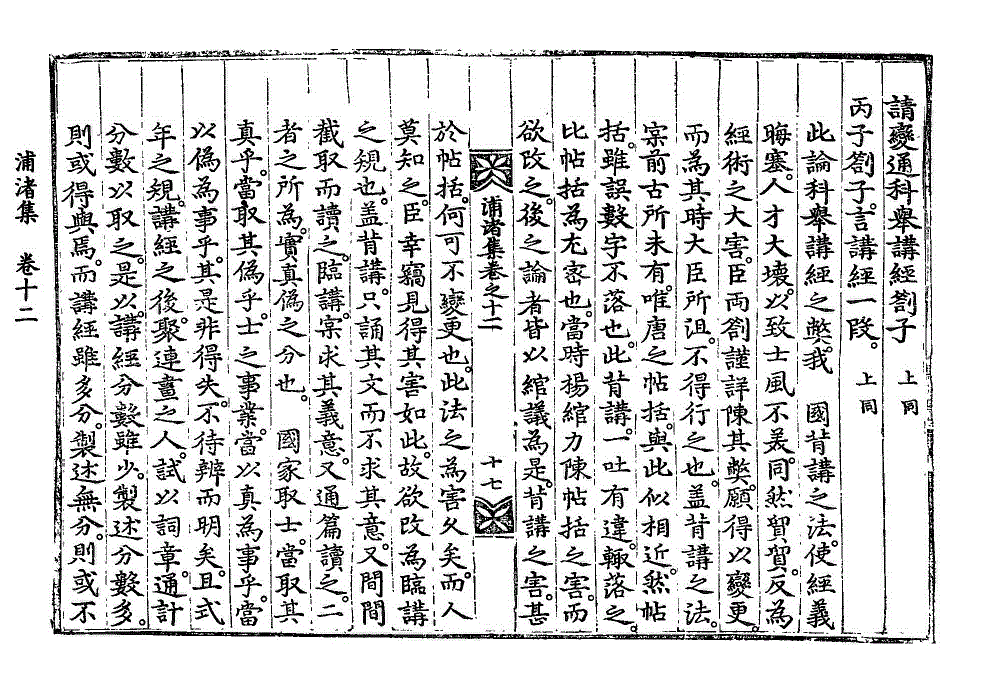 请变通科举讲经劄子(上同)
请变通科举讲经劄子(上同)丙子劄子。言讲经一段。(上同)
此论科举讲经之弊。我 国背讲之法。使经义晦塞。人才大坏。以致士风不美。同然贸贸。反为经术之大害。臣两劄谨详陈其弊。愿得以变更。而为其时大臣所沮。不得行之也。盖背讲之法。实前古所未有。唯唐之帖括。与此似相近。然帖括。虽误数字不落也。此背讲。一吐有违。辄落之。比帖括为尤密也。当时杨绾力陈帖括之害。而欲改之。后之论者皆以绾议为是。背讲之害。甚于帖括。何可不变更也。此法之为害久矣。而人莫知之。臣幸窃见得其害如此。故欲改为临讲之规也。盖背讲。只诵其文而不求其意。又间间截取而读之。临讲。实求其义意。又通篇读之。二者之所为。实真伪之分也。 国家取士。当取其真乎。当取其伪乎。士之事业。当以真为事乎。当以伪为事乎。其是非得失。不待辨而明矣。且式年之规。讲经之后。聚连画之人。试以词章。通计分数以取之。是以。讲经分数虽少。制述分数多。则或得与焉。而讲经虽多分。制述无分。则或不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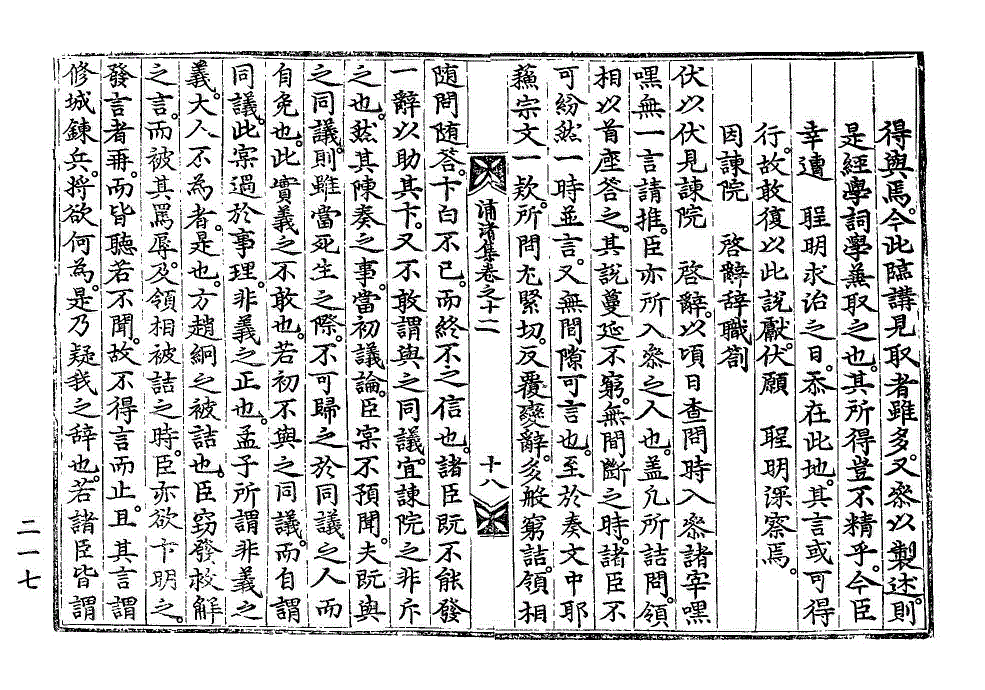 得与焉。今此临讲见取者虽多。又参以制述。则是经学词学兼取之也。其所得岂不精乎。今臣幸遭 圣明求治之日。忝在此地。其言或可得行。故敢复以此说献。伏愿 圣明深察焉。
得与焉。今此临讲见取者虽多。又参以制述。则是经学词学兼取之也。其所得岂不精乎。今臣幸遭 圣明求治之日。忝在此地。其言或可得行。故敢复以此说献。伏愿 圣明深察焉。因谏院 启辞辞职劄
伏以伏见谏院 启辞。以顷日查问时入参诸宰嘿嘿无一言请推。臣亦所入参之人也。盖凡所诘问。领相以首座答之。其说蔓延不穷。无间断之时。诸臣不可纷然一时并言。又无间隙可言也。至于奏文中耶苏宗文一款。所问尤紧切。反覆变辞。多般穷诘。领相随问随答。卞白不已。而终不之信也。诸臣既不能发一辞以助其卞。又不敢谓与之同议。宜谏院之非斥之也。然其陈奏之事。当初议论。臣实不预闻。夫既与之同议。则虽当死生之际。不可归之于同议之人而自免也。此实义之不敢也。若初不与之同议。而自谓同议。此实过于事理。非义之正也。孟子所谓非义之义。大人不为者。是也。方赵絅之被诘也。臣窃发救解之言。而被其骂辱。及领相被诘之时。臣亦欲卞明之。发言者再。而皆听若不闻。故不得言而止。且其言谓修城鍊兵。将欲何为。是乃疑我之辞也。若诸臣皆谓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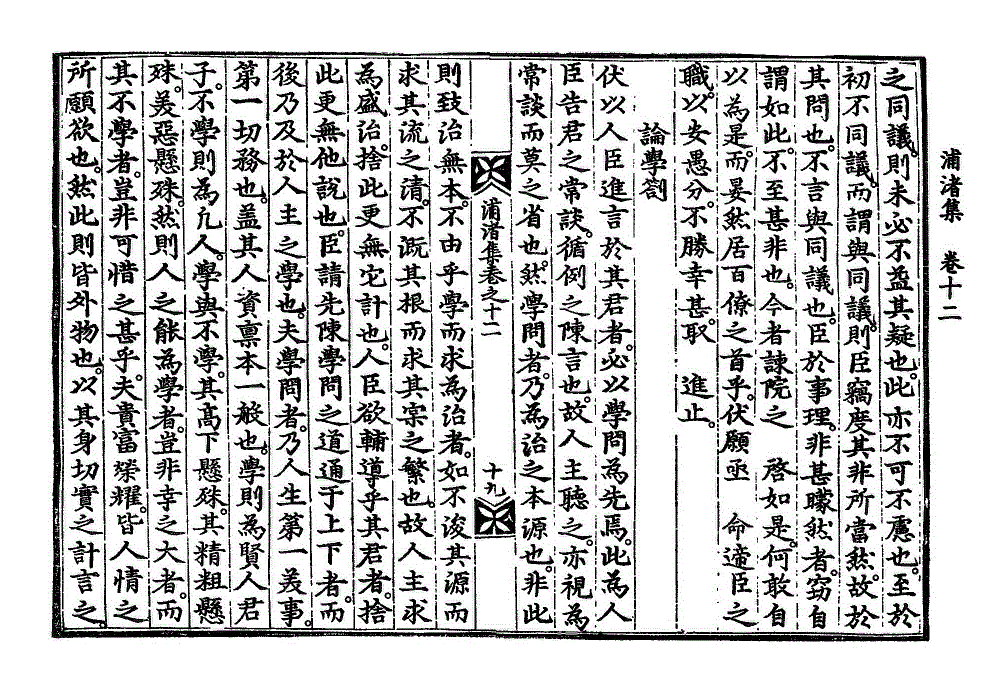 之同议。则未必不益其疑也。此亦不可不虑也。至于初不同议。而谓与同议。则臣窃度其非所当然。故于其问也。不言与同议也。臣于事理。非甚矇然者。窃自谓如此。不至甚非也。今者谏院之 启如是。何敢自以为是。而晏然居百僚之首乎。伏愿亟 命递臣之职。以安愚分。不胜幸甚。取 进止。
之同议。则未必不益其疑也。此亦不可不虑也。至于初不同议。而谓与同议。则臣窃度其非所当然。故于其问也。不言与同议也。臣于事理。非甚矇然者。窃自谓如此。不至甚非也。今者谏院之 启如是。何敢自以为是。而晏然居百僚之首乎。伏愿亟 命递臣之职。以安愚分。不胜幸甚。取 进止。论学劄
伏以人臣进言于其君者。必以学问为先焉。此为人臣告君之常谈。循例之陈言也。故人主听之。亦视为常谈而莫之省也。然学问者。乃为治之本源也。非此则致治无本。不由乎学而求为治者。如不浚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溉其根而求其实之繁也。故人主求为盛治。舍此更无它计也。人臣欲辅导乎其君者。舍此更无他说也。臣请先陈学问之道通于上下者。而后乃及于人主之学也。夫学问者。乃人生第一美事。第一切务也。盖其人资禀本一般也。学则为贤人君子。不学则为凡人。学与不学。其高下悬殊。其精粗悬殊。美恶悬殊。然则人之能为学者。岂非幸之大者。而其不学者。岂非可惜之甚乎。夫贵富荣耀。皆人情之所愿欲也。然此则皆外物也。以其身切实之计言之。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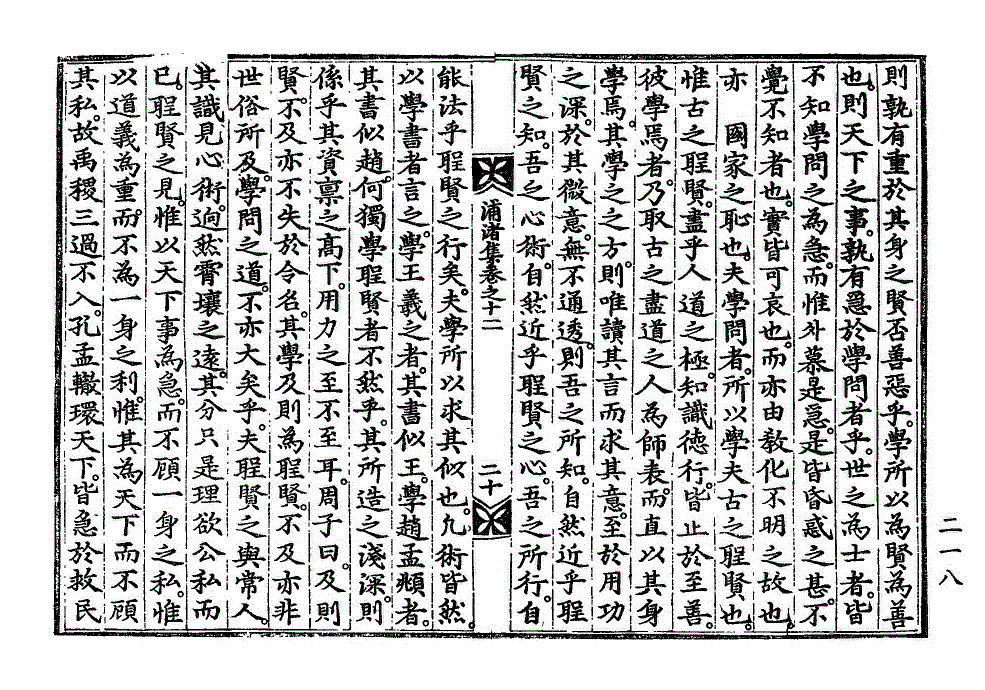 则孰有重于其身之贤否善恶乎。学所以为贤为善也。则天下之事。孰有急于学问者乎。世之为士者。皆不知学问之为急。而惟外慕是急。是皆昏惑之甚。不觉不知者也。实皆可哀也。而亦由教化不明之故也。亦 国家之耻也。夫学问者。所以学夫古之圣贤也。惟古之圣贤。尽乎人道之极。知识德行。皆止于至善。彼学焉者。乃取古之尽道之人为师表。而直以其身学焉。其学之之方。则唯读其言而求其意。至于用功之深。于其微意。无不通透。则吾之所知。自然近乎圣贤之知。吾之心术。自然近乎圣贤之心。吾之所行。自能法乎圣贤之行矣。夫学所以求其似也。凡术皆然。以学书者言之。学王羲之者。其书似王。学赵孟頫者。其书似赵。何独学圣贤者不然乎。其所造之浅深。则系乎其资禀之高下。用力之至不至耳。周子曰。及则贤。不及亦不失于令名。其学及则为圣贤。不及亦非世俗所及。学问之道。不亦大矣乎。夫圣贤之与常人。其识见心术。迥然霄壤之远。其分只是理欲公私而已。圣贤之见。惟以天下事为急。而不顾一身之私。惟以道义为重。而不为一身之利。惟其为天下而不顾其私。故禹稷三过不入。孔孟辙环天下。皆急于救民
则孰有重于其身之贤否善恶乎。学所以为贤为善也。则天下之事。孰有急于学问者乎。世之为士者。皆不知学问之为急。而惟外慕是急。是皆昏惑之甚。不觉不知者也。实皆可哀也。而亦由教化不明之故也。亦 国家之耻也。夫学问者。所以学夫古之圣贤也。惟古之圣贤。尽乎人道之极。知识德行。皆止于至善。彼学焉者。乃取古之尽道之人为师表。而直以其身学焉。其学之之方。则唯读其言而求其意。至于用功之深。于其微意。无不通透。则吾之所知。自然近乎圣贤之知。吾之心术。自然近乎圣贤之心。吾之所行。自能法乎圣贤之行矣。夫学所以求其似也。凡术皆然。以学书者言之。学王羲之者。其书似王。学赵孟頫者。其书似赵。何独学圣贤者不然乎。其所造之浅深。则系乎其资禀之高下。用力之至不至耳。周子曰。及则贤。不及亦不失于令名。其学及则为圣贤。不及亦非世俗所及。学问之道。不亦大矣乎。夫圣贤之与常人。其识见心术。迥然霄壤之远。其分只是理欲公私而已。圣贤之见。惟以天下事为急。而不顾一身之私。惟以道义为重。而不为一身之利。惟其为天下而不顾其私。故禹稷三过不入。孔孟辙环天下。皆急于救民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19H 页
 也。唯以道义为重。而不为其利。故天下之禄。千驷之富。非义则不视也。至于躯命之重。当不义则舍之。其大公至正为如何哉。常人只见其一身之重。故其心之所存。只为其得失利害之私而已。其平生营营尽其心力者。惟在于此。其视圣贤之公正。岂不远哉。其间虽或有质美之人不为非义者。其规模意思。终不能免于私也。夫均人也。均有此理。其中美质者亦自不少。苟自求之。皆可以为贤人君子。只为学术不明。同然自弃。为庸陋狭小之归。可胜惜哉。人苟知此则何可不以圣贤之学为事。而唯事乎求利之习哉。国家之教育。何可不以圣贤之学导之。而唯导之以求利之习哉。夫人主之学。亦何以异于此乎。古之圣人。履至尊之位。以至德行至治者。如二帝如三王是也。其德其治。当为万世之师法。后之人君。惟当以二帝三王为师表而法之。二帝三王言论政事。载在方册。今皆可见。苟能读而求之。凡其精一之法。儆戒之严。知人之哲。爱民之仁。一一效而为之。无一不法乎此。则德何以不及于古。治何以不及于古乎。学之道。何以加于此乎。然古之帝王。世代既远。文籍简约。其传于后者。不博。唯孔孟之学。祖述宪章。远继其统。前圣
也。唯以道义为重。而不为其利。故天下之禄。千驷之富。非义则不视也。至于躯命之重。当不义则舍之。其大公至正为如何哉。常人只见其一身之重。故其心之所存。只为其得失利害之私而已。其平生营营尽其心力者。惟在于此。其视圣贤之公正。岂不远哉。其间虽或有质美之人不为非义者。其规模意思。终不能免于私也。夫均人也。均有此理。其中美质者亦自不少。苟自求之。皆可以为贤人君子。只为学术不明。同然自弃。为庸陋狭小之归。可胜惜哉。人苟知此则何可不以圣贤之学为事。而唯事乎求利之习哉。国家之教育。何可不以圣贤之学导之。而唯导之以求利之习哉。夫人主之学。亦何以异于此乎。古之圣人。履至尊之位。以至德行至治者。如二帝如三王是也。其德其治。当为万世之师法。后之人君。惟当以二帝三王为师表而法之。二帝三王言论政事。载在方册。今皆可见。苟能读而求之。凡其精一之法。儆戒之严。知人之哲。爱民之仁。一一效而为之。无一不法乎此。则德何以不及于古。治何以不及于古乎。学之道。何以加于此乎。然古之帝王。世代既远。文籍简约。其传于后者。不博。唯孔孟之学。祖述宪章。远继其统。前圣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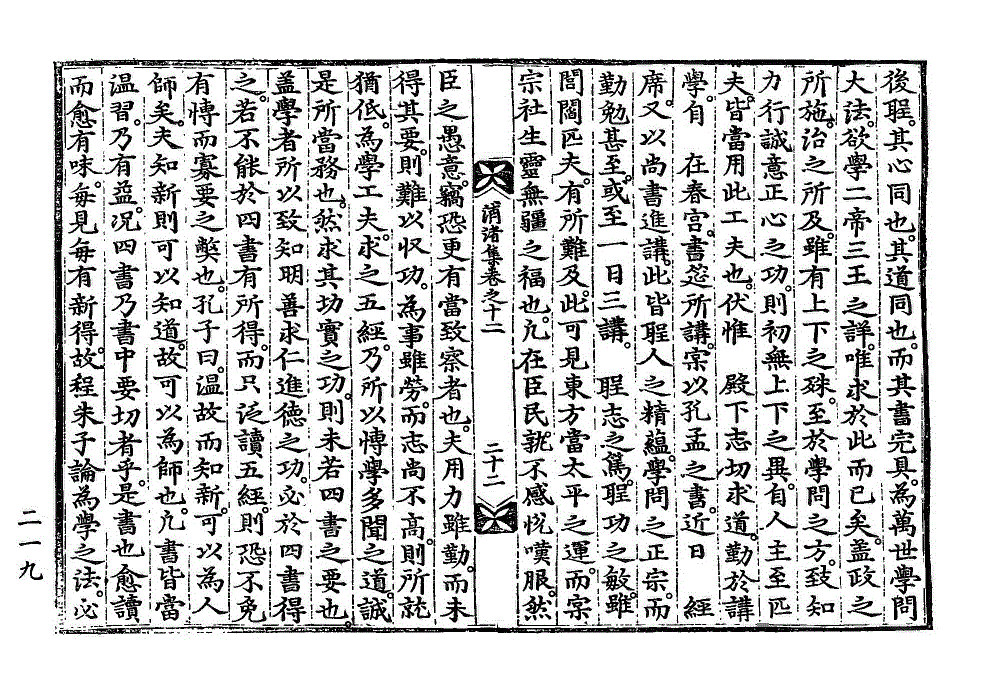 后圣。其心同也。其道同也。而其书完具。为万世学问大法。欲学二帝三王之详。唯求于此而已矣。盖政之所施。治之所及。虽有上下之殊。至于学问之方。致知力行诚意正心之功。则初无上下之异。自人主至匹夫。皆当用此工夫也。伏惟 殿下志切求道。勤于讲学。自 在春宫。书筵所讲。实以孔孟之书。近日 经席。又以尚书进讲。此皆圣人之精蕴。学问之正宗。而勤勉甚至。或至一日三讲。 圣志之笃。圣功之敏。虽闾阎匹夫。有所难及。此可见东方当太平之运。而实宗社生灵无疆之福也。凡在臣民。孰不感悦叹服。然臣之愚意。窃恐更有当致察者也。夫用力虽勤。而未得其要。则难以收功。为事虽劳。而志尚不高。则所就犹低。为学工夫。求之五经。乃所以博学多闻之道。诚是所当务也。然求其切实之功。则未若四书之要也。盖学者所以致知明善求仁进德之功。必于四书得之。若不能于四书有所得。而只泛读五经。则恐不免有博而寡要之弊也。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人师矣。夫知新则可以知道。故可以为师也。凡书皆当温习。乃有益。况四书乃书中要切者乎。是书也愈读而愈有味。每见每有新得。故程朱子论为学之法。必
后圣。其心同也。其道同也。而其书完具。为万世学问大法。欲学二帝三王之详。唯求于此而已矣。盖政之所施。治之所及。虽有上下之殊。至于学问之方。致知力行诚意正心之功。则初无上下之异。自人主至匹夫。皆当用此工夫也。伏惟 殿下志切求道。勤于讲学。自 在春宫。书筵所讲。实以孔孟之书。近日 经席。又以尚书进讲。此皆圣人之精蕴。学问之正宗。而勤勉甚至。或至一日三讲。 圣志之笃。圣功之敏。虽闾阎匹夫。有所难及。此可见东方当太平之运。而实宗社生灵无疆之福也。凡在臣民。孰不感悦叹服。然臣之愚意。窃恐更有当致察者也。夫用力虽勤。而未得其要。则难以收功。为事虽劳。而志尚不高。则所就犹低。为学工夫。求之五经。乃所以博学多闻之道。诚是所当务也。然求其切实之功。则未若四书之要也。盖学者所以致知明善求仁进德之功。必于四书得之。若不能于四书有所得。而只泛读五经。则恐不免有博而寡要之弊也。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人师矣。夫知新则可以知道。故可以为师也。凡书皆当温习。乃有益。况四书乃书中要切者乎。是书也愈读而愈有味。每见每有新得。故程朱子论为学之法。必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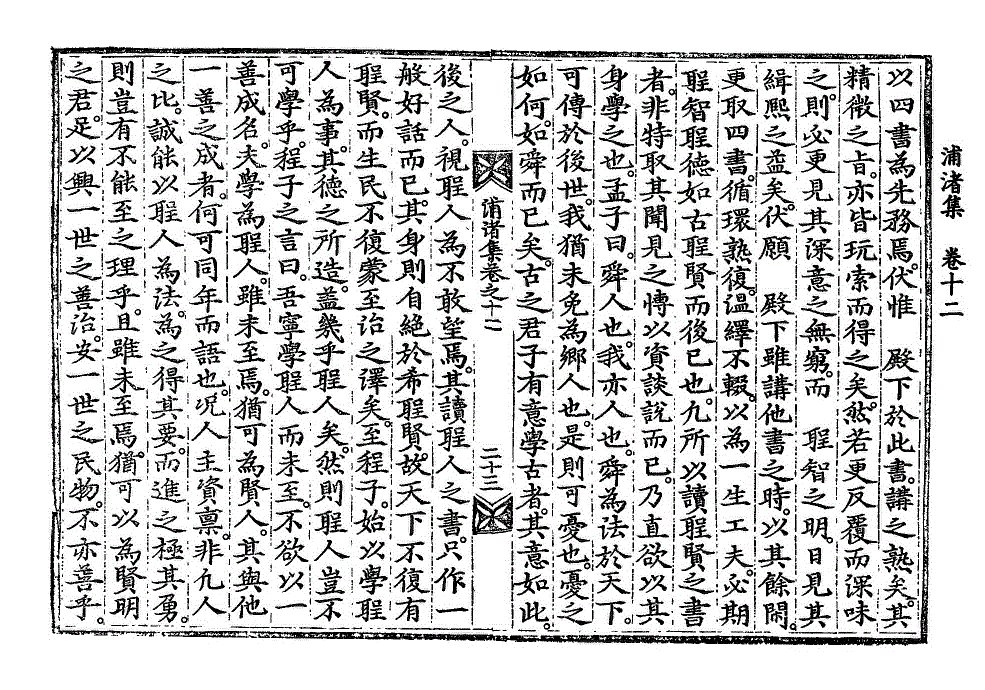 以四书为先务焉。伏惟 殿下于此书。讲之熟矣。其精微之旨。亦皆玩索而得之矣。然若更反覆而深味之。则必更见其深意之无穷。而 圣智之明。日见其缉熙之益矣。伏愿 殿下虽讲他书之时。以其馀闲。更取四书。循环熟复。温绎不辍。以为一生工夫。必期圣智圣德如古圣贤而后已也。凡所以读圣贤之书者。非特取其闻见之博以资谈说而已。乃直欲以其身学之也。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古之君子有意学古者。其意如此。后之人。视圣人为不敢望焉。其读圣人之书。只作一般好话而已。其身则自绝于希圣贤。故天下不复有圣贤。而生民不复蒙至治之泽矣。至程子。始以学圣人为事。其德之所造。盖几乎圣人矣。然则圣人岂不可学乎。程子之言曰。吾宁学圣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夫学为圣人。虽未至焉。犹可为贤人。其与他一善之成者。何可同年而语也。况人主资禀。非凡人之比。诚能以圣人为法。为之得其要。而进之极其勇。则岂有不能至之理乎。且虽未至焉。犹可以为贤明之君。足以兴一世之善治。安一世之民物。不亦善乎。
以四书为先务焉。伏惟 殿下于此书。讲之熟矣。其精微之旨。亦皆玩索而得之矣。然若更反覆而深味之。则必更见其深意之无穷。而 圣智之明。日见其缉熙之益矣。伏愿 殿下虽讲他书之时。以其馀闲。更取四书。循环熟复。温绎不辍。以为一生工夫。必期圣智圣德如古圣贤而后已也。凡所以读圣贤之书者。非特取其闻见之博以资谈说而已。乃直欲以其身学之也。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古之君子有意学古者。其意如此。后之人。视圣人为不敢望焉。其读圣人之书。只作一般好话而已。其身则自绝于希圣贤。故天下不复有圣贤。而生民不复蒙至治之泽矣。至程子。始以学圣人为事。其德之所造。盖几乎圣人矣。然则圣人岂不可学乎。程子之言曰。吾宁学圣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夫学为圣人。虽未至焉。犹可为贤人。其与他一善之成者。何可同年而语也。况人主资禀。非凡人之比。诚能以圣人为法。为之得其要。而进之极其勇。则岂有不能至之理乎。且虽未至焉。犹可以为贤明之君。足以兴一世之善治。安一世之民物。不亦善乎。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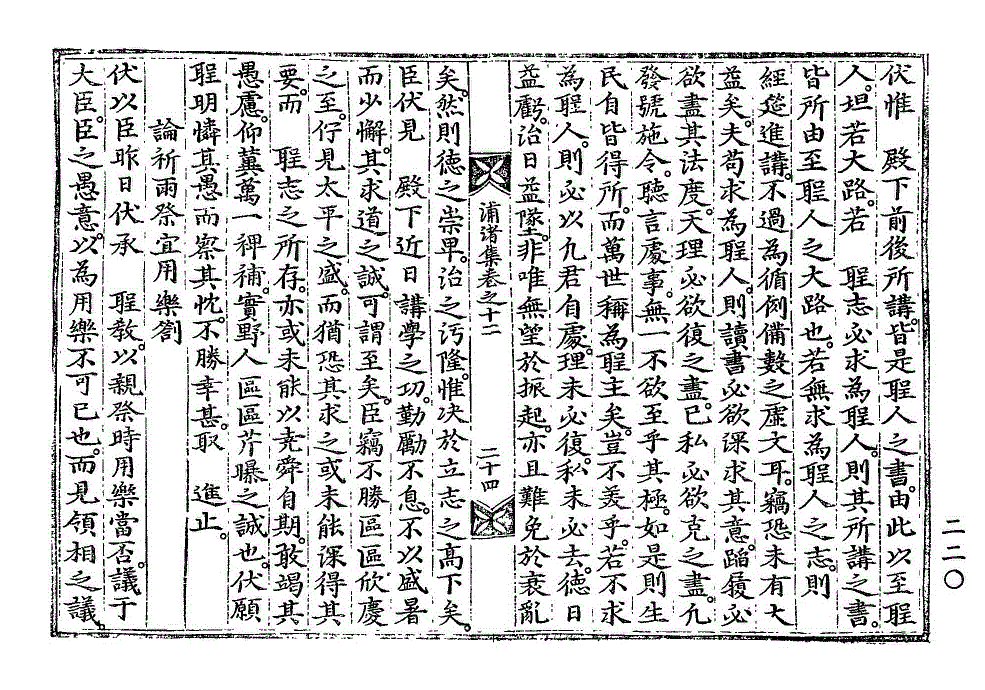 伏惟 殿下前后所讲。皆是圣人之书。由此以至圣人。坦若大路。若 圣志必求为圣人。则其所讲之书。皆所由至圣人之大路也。若无求为圣人之志。则 经筵进讲。不过为循例备数之虚文耳。窃恐未有大益矣。夫苟求为圣人。则读书必欲深求其意。蹈履必欲尽其法度。天理必欲复之尽。己私必欲克之尽。凡发号施令。听言处事。无一不欲至乎其极。如是则生民自皆得所。而万世称为圣主矣。岂不美乎。若不求为圣人。则必以凡君自处。理未必复。私未必去。德日益亏。治日益坠。非唯无望于振起。亦且难免于衰乱矣。然则德之崇卑。治之污隆。惟决于立志之高下矣。臣伏见 殿下近日讲学之功。勤励不息。不以盛暑而少懈。其求道之诚。可谓至矣。臣窃不胜区区欣庆之至。伫见太平之盛。而犹恐其求之或未能深得其要。而 圣志之所存。亦或未能以尧舜自期。敢竭其愚虑。仰冀万一裨补。实野人区区芹曝之诚也。伏愿圣明怜其愚而察其忱。不胜幸甚。取 进止。
伏惟 殿下前后所讲。皆是圣人之书。由此以至圣人。坦若大路。若 圣志必求为圣人。则其所讲之书。皆所由至圣人之大路也。若无求为圣人之志。则 经筵进讲。不过为循例备数之虚文耳。窃恐未有大益矣。夫苟求为圣人。则读书必欲深求其意。蹈履必欲尽其法度。天理必欲复之尽。己私必欲克之尽。凡发号施令。听言处事。无一不欲至乎其极。如是则生民自皆得所。而万世称为圣主矣。岂不美乎。若不求为圣人。则必以凡君自处。理未必复。私未必去。德日益亏。治日益坠。非唯无望于振起。亦且难免于衰乱矣。然则德之崇卑。治之污隆。惟决于立志之高下矣。臣伏见 殿下近日讲学之功。勤励不息。不以盛暑而少懈。其求道之诚。可谓至矣。臣窃不胜区区欣庆之至。伫见太平之盛。而犹恐其求之或未能深得其要。而 圣志之所存。亦或未能以尧舜自期。敢竭其愚虑。仰冀万一裨补。实野人区区芹曝之诚也。伏愿圣明怜其愚而察其忱。不胜幸甚。取 进止。论祈雨祭宜用乐劄
伏以臣昨日伏承 圣教。以亲祭时用乐当否。议于大臣。臣之愚意。以为用乐不可已也。而见领相之议。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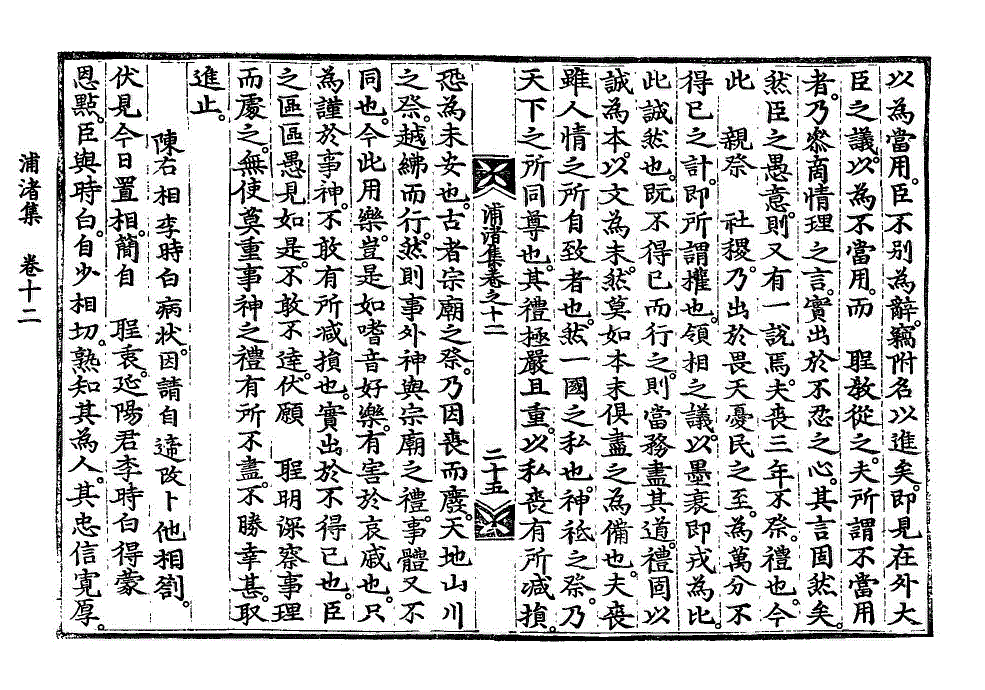 以为当用。臣不别为辞。窃附名以进矣。即见在外大臣之议。以为不当用。而 圣教从之。夫所谓不当用者。乃参商情理之言。实出于不忍之心。其言固然矣。然臣之愚意。则又有一说焉。夫丧三年不祭。礼也。今此 亲祭 社稷。乃出于畏天忧民之至。为万分不得已之计。即所谓权也。领相之议。以墨衰即戎为比。此诚然也。既不得已而行之。则当务尽其道。礼固以诚为本。以文为末。然莫如本末俱尽之为备也。夫丧虽人情之所自致者也。然一国之私也。神祗之祭。乃天下之所同尊也。其礼极严且重。以私丧有所减损。恐为未安也。古者宗庙之祭。乃因丧而废。天地山川之祭。越绋而行。然则事外神与宗庙之礼。事体又不同也。今此用乐。岂是如嗜音好乐。有害于哀戚也。只为谨于事神。不敢有所减损也。实出于不得已也。臣之区区愚见如是。不敢不达。伏愿 圣明深察事理而处之。无使莫重事神之礼有所不尽。不胜幸甚。取进止。
以为当用。臣不别为辞。窃附名以进矣。即见在外大臣之议。以为不当用。而 圣教从之。夫所谓不当用者。乃参商情理之言。实出于不忍之心。其言固然矣。然臣之愚意。则又有一说焉。夫丧三年不祭。礼也。今此 亲祭 社稷。乃出于畏天忧民之至。为万分不得已之计。即所谓权也。领相之议。以墨衰即戎为比。此诚然也。既不得已而行之。则当务尽其道。礼固以诚为本。以文为末。然莫如本末俱尽之为备也。夫丧虽人情之所自致者也。然一国之私也。神祗之祭。乃天下之所同尊也。其礼极严且重。以私丧有所减损。恐为未安也。古者宗庙之祭。乃因丧而废。天地山川之祭。越绋而行。然则事外神与宗庙之礼。事体又不同也。今此用乐。岂是如嗜音好乐。有害于哀戚也。只为谨于事神。不敢有所减损也。实出于不得已也。臣之区区愚见如是。不敢不达。伏愿 圣明深察事理而处之。无使莫重事神之礼有所不尽。不胜幸甚。取进止。陈右相李时白病状。因请自递改卜他相劄。
伏见今日置相。简自 圣衷。延阳君李时白得蒙 恩点。臣与时白。自少相切。熟知其为人。其忠信宽厚。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21L 页
 廉谨好义。虑事周密。在诸臣中鲜有其比。此群臣之所共知也。 睿简及此。窃见群臣忠邪贤否。莫能逃于 圣鉴也。凡在瞻聆。孰不仰服 圣上知人之明。而喜宰相之得人也。然臣之所忧虑。实甚于喜悦。何者。其人自少筋骨则强壮过人。而气甚虚惫。少或失摄。则感疾常速。且其平生。尽诚居官。又累经艰险。费心力太甚。到今衰老。疾病深痼。此亦群臣之所共知也。今又有陈奏之 命。以七十多病之人。万里行役。其不能无事得达决矣。非但其人疾病为可虑。 国家陈奏之事。极重且急。而必至迟滞。不得以时将命。此岂非尤可虑者乎。且其忠虑可恃。 圣意亦必倚重。岂可使暂离 朝廷乎。百尔思之。如臣老病不足为有无者。宜退处闲地。以调残疾。而更卜年少可堪远行之人。令奉 命以行。窃恐计无便于此也。如臣迂拙无能。在位实为无益。且臣虽在原任之列。 国家大事。何所不与闻。苟其区区思虑或有补于当时者。何敢以在闲地。而不尽其愚乎。且臣与右相为婚家。例当相避。而右相爰立方新。不宜即递。臣在位日久。衰病已甚。从前乞退者。屡矣。今其退也。正得其时也。伏愿 圣明熟察臣之愚虑实为今日切计。即许
廉谨好义。虑事周密。在诸臣中鲜有其比。此群臣之所共知也。 睿简及此。窃见群臣忠邪贤否。莫能逃于 圣鉴也。凡在瞻聆。孰不仰服 圣上知人之明。而喜宰相之得人也。然臣之所忧虑。实甚于喜悦。何者。其人自少筋骨则强壮过人。而气甚虚惫。少或失摄。则感疾常速。且其平生。尽诚居官。又累经艰险。费心力太甚。到今衰老。疾病深痼。此亦群臣之所共知也。今又有陈奏之 命。以七十多病之人。万里行役。其不能无事得达决矣。非但其人疾病为可虑。 国家陈奏之事。极重且急。而必至迟滞。不得以时将命。此岂非尤可虑者乎。且其忠虑可恃。 圣意亦必倚重。岂可使暂离 朝廷乎。百尔思之。如臣老病不足为有无者。宜退处闲地。以调残疾。而更卜年少可堪远行之人。令奉 命以行。窃恐计无便于此也。如臣迂拙无能。在位实为无益。且臣虽在原任之列。 国家大事。何所不与闻。苟其区区思虑或有补于当时者。何敢以在闲地。而不尽其愚乎。且臣与右相为婚家。例当相避。而右相爰立方新。不宜即递。臣在位日久。衰病已甚。从前乞退者。屡矣。今其退也。正得其时也。伏愿 圣明熟察臣之愚虑实为今日切计。即许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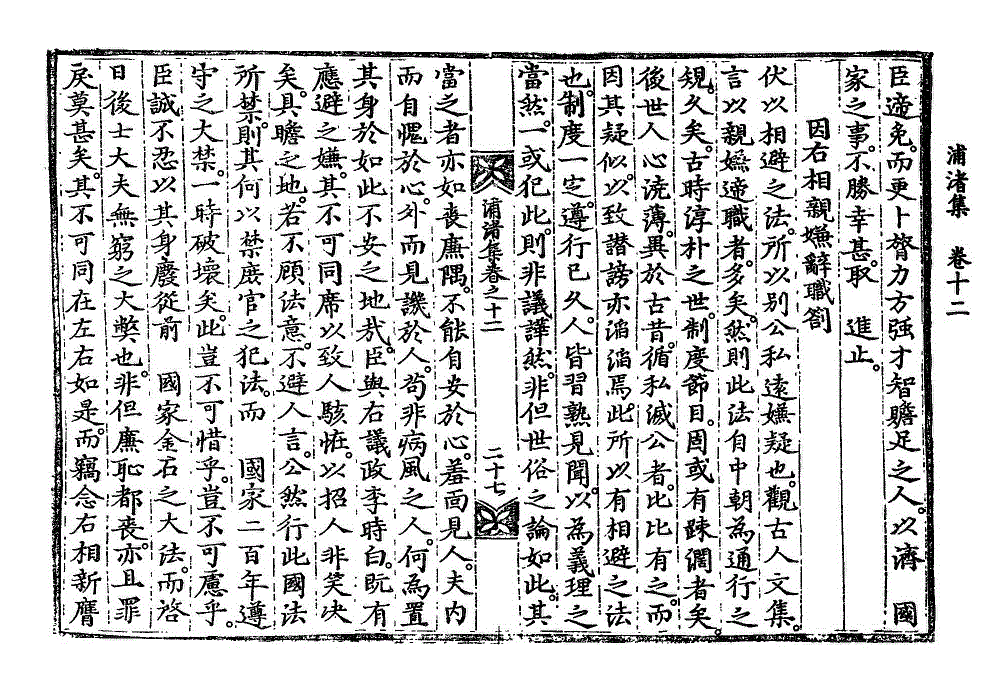 臣递免。而更卜膂力方强才智赡足之人。以济 国家之事。不胜幸甚。取 进止。
臣递免。而更卜膂力方强才智赡足之人。以济 国家之事。不胜幸甚。取 进止。因右相亲嫌辞职劄
伏以相避之法。所以别公私远嫌疑也。观古人文集。言以亲嫌递职者。多矣。然则此法自中朝为通行之规。久矣。古时淳朴之世。制度节目。固或有疏阔者矣。后世人心浇薄。异于古昔。循私灭公者。比比有之。而因其疑似。以致谮谤亦滔滔焉。此所以有相避之法也。制度一定。遵行已久。人皆习熟见闻。以为义理之当然。一或犯此。则非议哗然。非但世俗之论如此。其当之者亦如丧廉隅。不能自安于心。羞面见人。夫内而自愧于心。外而见讥于人。苟非病风之人。何为置其身于如此不安之地哉。臣与右议政李时白。既有应避之嫌。其不可同席以致人骇怪。以招人非笑决矣。具瞻之地。若不顾法意。不避人言。公然行此国法所禁。则其何以禁庶官之犯法。而 国家二百年遵守之大禁。一时破坏矣。此岂不可惜乎。岂不可虑乎。臣诚不忍以其身废从前 国家金石之大法。而启日后士大夫无穷之大弊也。非但廉耻都丧。亦且罪戾莫甚矣。其不可同在左右如是。而窃念右相新膺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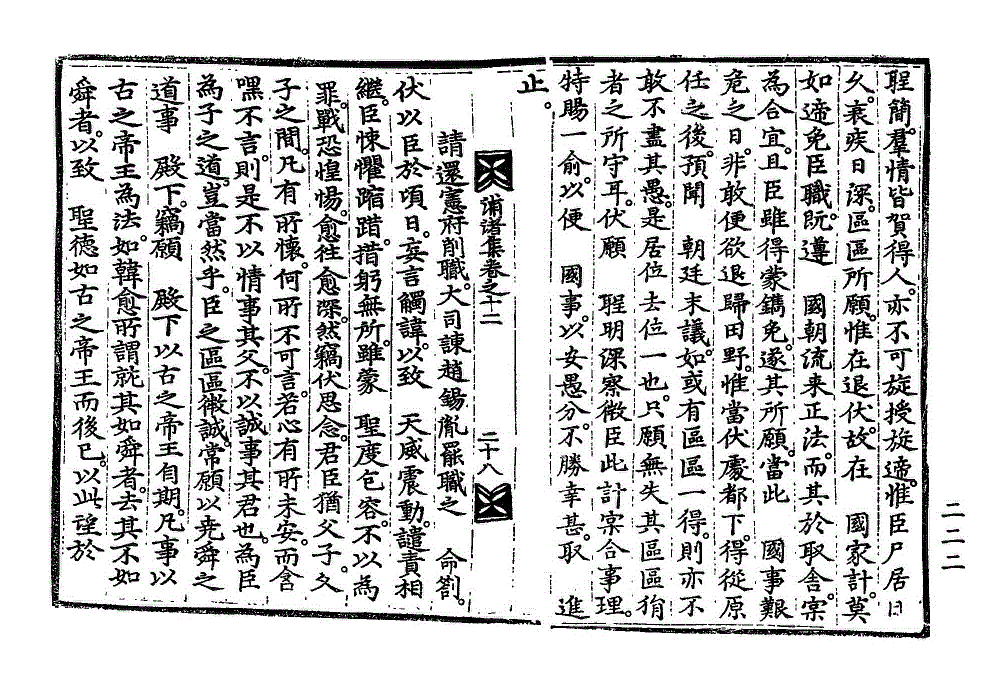 圣简。群情皆贺得人。亦不可旋授旋递。惟臣尸居日久。衰疾日深。区区所愿。惟在退伏。故在 国家计。莫如递免臣职。既遵 国朝流来正法。而其于取舍。实为合宜。且臣虽得蒙镌免。遂其所愿。当此 国事艰危之日。非敢便欲退归田野。惟当伏处都下。得从原任之后。预闻 朝廷末议。如或有区区一得。则亦不敢不尽其愚。是居位去位一也。只愿无失其区区狷者之所守耳。伏愿 圣明深察微臣此计实合事理。特赐一俞。以便 国事。以安愚分。不胜幸甚。取 进止。
圣简。群情皆贺得人。亦不可旋授旋递。惟臣尸居日久。衰疾日深。区区所愿。惟在退伏。故在 国家计。莫如递免臣职。既遵 国朝流来正法。而其于取舍。实为合宜。且臣虽得蒙镌免。遂其所愿。当此 国事艰危之日。非敢便欲退归田野。惟当伏处都下。得从原任之后。预闻 朝廷末议。如或有区区一得。则亦不敢不尽其愚。是居位去位一也。只愿无失其区区狷者之所守耳。伏愿 圣明深察微臣此计实合事理。特赐一俞。以便 国事。以安愚分。不胜幸甚。取 进止。请还宪府削职。大司谏赵锡胤罢职之 命劄。
伏以臣于顷日。妄言触讳。以致 天威震动。谴责相继。臣悚惧蹜踖。措躬无所。虽蒙 圣度包容。不以为罪。战恐惶惕。愈往愈深。然窃伏思念。君臣犹父子。父子之间。凡有所怀。何所不可言。若心有所未安。而含默不言。则是不以情事其父。不以诚事其君也。为臣为子之道。岂当然乎。臣之区区微诚。常愿以尧舜之道事 殿下。窃愿 殿下以古之帝王自期。凡事以古之帝王为法。如韩愈所谓就其如舜者。去其不如舜者。以致 圣德如古之帝王而后已。以此望于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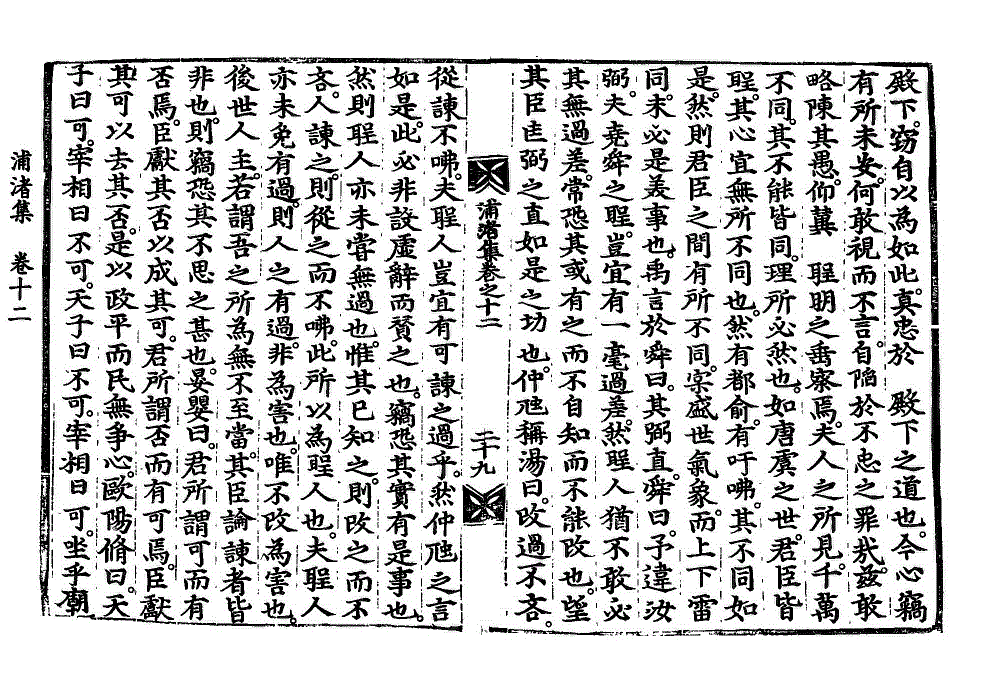 殿下。窃自以为如此。真忠于 殿下之道也。今心窃有所未安。何敢视而不言。自陷于不忠之罪哉。兹敢略陈其愚。仰冀 圣明之垂察焉。夫人之所见。千万不同。其不能皆同。理所必然也。如唐虞之世。君臣皆圣。其心宜无所不同也。然有都俞。有吁咈。其不同如是。然则君臣之间有所不同。实盛世气象。而上下雷同。未必是美事也。禹言于舜曰。其弼直。舜曰。予违汝弼。夫尧舜之圣。岂宜有一毫过差。然圣人犹不敢必其无过差。常恐其或有之而不自知而不能改也。望其臣匡弼之直如是之切也。仲虺称汤曰。改过不吝。从谏不咈。夫圣人岂宜有可谏之过乎。然仲虺之言如是。此必非设虚辞而赞之也。窃恐其实有是事也。然则圣人亦未尝无过也。惟其已知之。则改之而不吝。人谏之。则从之而不咈。此所以为圣人也。夫圣人亦未免有过。则人之有过。非为害也。唯不改为害也。后世人主。若谓吾之所为无不至当。其臣论谏者皆非也。则窃恐其不思之甚也。晏婴曰。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民无争心。欧阳脩曰。天子曰可。宰相曰不可。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坐乎庙
殿下。窃自以为如此。真忠于 殿下之道也。今心窃有所未安。何敢视而不言。自陷于不忠之罪哉。兹敢略陈其愚。仰冀 圣明之垂察焉。夫人之所见。千万不同。其不能皆同。理所必然也。如唐虞之世。君臣皆圣。其心宜无所不同也。然有都俞。有吁咈。其不同如是。然则君臣之间有所不同。实盛世气象。而上下雷同。未必是美事也。禹言于舜曰。其弼直。舜曰。予违汝弼。夫尧舜之圣。岂宜有一毫过差。然圣人犹不敢必其无过差。常恐其或有之而不自知而不能改也。望其臣匡弼之直如是之切也。仲虺称汤曰。改过不吝。从谏不咈。夫圣人岂宜有可谏之过乎。然仲虺之言如是。此必非设虚辞而赞之也。窃恐其实有是事也。然则圣人亦未尝无过也。惟其已知之。则改之而不吝。人谏之。则从之而不咈。此所以为圣人也。夫圣人亦未免有过。则人之有过。非为害也。唯不改为害也。后世人主。若谓吾之所为无不至当。其臣论谏者皆非也。则窃恐其不思之甚也。晏婴曰。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民无争心。欧阳脩曰。天子曰可。宰相曰不可。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坐乎庙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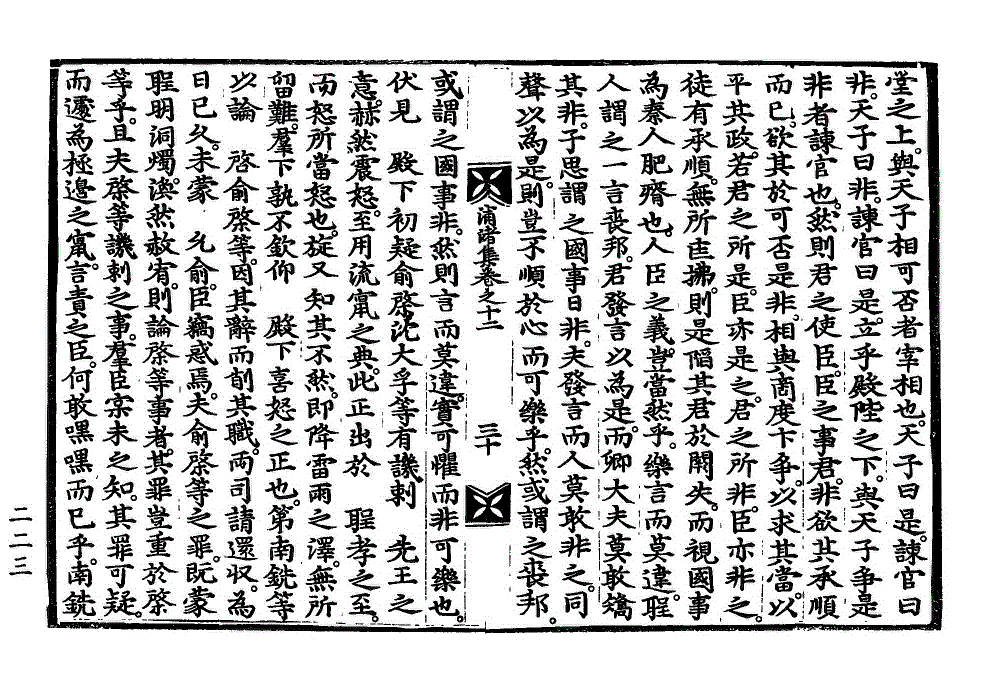 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非。谏官曰是。立乎殿陛之下。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然则君之使臣。臣之事君。非欲其承顺而已。欲其于可否是非。相与商度卞争。以求其当。以平其政。若君之所是。臣亦是之。君之所非。臣亦非之。徒有承顺。无所匡拂。则是陷其君于阙失。而视国事为秦人肥瘠也。人臣之义。岂当然乎。乐言而莫违。圣人谓之一言丧邦。君发言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子思谓之国事日非。夫发言而人莫敢非之。同声以为是。则岂不顺于心而可乐乎。然或谓之丧邦。或谓之国事非。然则言而莫违。实可惧而非可乐也。伏见 殿下初疑俞棨,沈大孚等有讥刺 先王之意。赫然震怒。至用流窜之典。此正出于 圣孝之至。而怒所当怒也。旋又知其不然。即降雷雨之泽。无所留难。群下孰不钦仰 殿下喜怒之正也。第南铣等以论 启俞棨等。因其辞而削其职。两司请还收。为日已久。未蒙 允俞。臣窃惑焉。夫俞棨等之罪。既蒙圣明洞烛。涣然赦宥。则论棨等事者。其罪岂重于棨等乎。且夫棨等讥刺之事。群臣实未之知。其罪可疑。而遽为极边之窜。言责之臣。何敢默默而已乎。南铣
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非。谏官曰是。立乎殿陛之下。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然则君之使臣。臣之事君。非欲其承顺而已。欲其于可否是非。相与商度卞争。以求其当。以平其政。若君之所是。臣亦是之。君之所非。臣亦非之。徒有承顺。无所匡拂。则是陷其君于阙失。而视国事为秦人肥瘠也。人臣之义。岂当然乎。乐言而莫违。圣人谓之一言丧邦。君发言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子思谓之国事日非。夫发言而人莫敢非之。同声以为是。则岂不顺于心而可乐乎。然或谓之丧邦。或谓之国事非。然则言而莫违。实可惧而非可乐也。伏见 殿下初疑俞棨,沈大孚等有讥刺 先王之意。赫然震怒。至用流窜之典。此正出于 圣孝之至。而怒所当怒也。旋又知其不然。即降雷雨之泽。无所留难。群下孰不钦仰 殿下喜怒之正也。第南铣等以论 启俞棨等。因其辞而削其职。两司请还收。为日已久。未蒙 允俞。臣窃惑焉。夫俞棨等之罪。既蒙圣明洞烛。涣然赦宥。则论棨等事者。其罪岂重于棨等乎。且夫棨等讥刺之事。群臣实未之知。其罪可疑。而遽为极边之窜。言责之臣。何敢默默而已乎。南铣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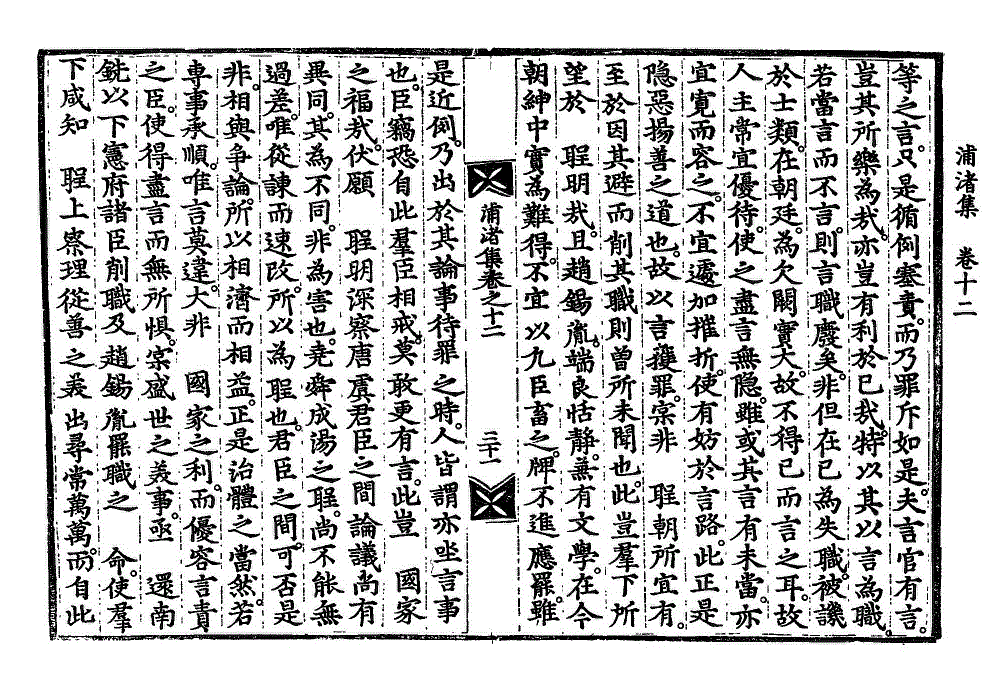 等之言。只是循例塞责。而乃罪斥如是。夫言官有言。岂其所乐为哉。亦岂有利于己哉。特以其以言为职。若当言而不言。则言职废矣。非但在己为失职。被讥于士类。在朝廷。为欠阙实大。故不得已而言之耳。故人主常宜优待。使之尽言无隐。虽或其言有未当。亦宜宽而容之。不宜遽加摧折。使有妨于言路。此正是隐恶扬善之道也。故以言获罪。实非 圣朝所宜有。至于因其避而削其职则曾所未闻也。此岂群下所望于 圣明哉。且赵锡胤。端良恬静。兼有文学。在今朝绅中实为难得。不宜以凡臣畜之。牌不进应罢。虽是近例。乃出于其论事待罪之时。人皆谓亦坐言事也。臣窃恐自此群臣相戒。莫敢更有言。此岂 国家之福哉。伏愿 圣明深察唐虞君臣之间论议尚有异同。其为不同。非为害也。尧舜成汤之圣。尚不能无过差。唯从谏而速改。所以为圣也。君臣之间。可否是非。相与争论。所以相济而相益。正是治体之当然。若专事承顺。唯言莫违。大非 国家之利。而优容言责之臣。使得尽言而无所惧。实盛世之美事。亟 还南铣以下宪府诸臣削职及赵锡胤罢职之 命。使群下咸知 圣上察理从善之美出寻常万万。而自此
等之言。只是循例塞责。而乃罪斥如是。夫言官有言。岂其所乐为哉。亦岂有利于己哉。特以其以言为职。若当言而不言。则言职废矣。非但在己为失职。被讥于士类。在朝廷。为欠阙实大。故不得已而言之耳。故人主常宜优待。使之尽言无隐。虽或其言有未当。亦宜宽而容之。不宜遽加摧折。使有妨于言路。此正是隐恶扬善之道也。故以言获罪。实非 圣朝所宜有。至于因其避而削其职则曾所未闻也。此岂群下所望于 圣明哉。且赵锡胤。端良恬静。兼有文学。在今朝绅中实为难得。不宜以凡臣畜之。牌不进应罢。虽是近例。乃出于其论事待罪之时。人皆谓亦坐言事也。臣窃恐自此群臣相戒。莫敢更有言。此岂 国家之福哉。伏愿 圣明深察唐虞君臣之间论议尚有异同。其为不同。非为害也。尧舜成汤之圣。尚不能无过差。唯从谏而速改。所以为圣也。君臣之间。可否是非。相与争论。所以相济而相益。正是治体之当然。若专事承顺。唯言莫违。大非 国家之利。而优容言责之臣。使得尽言而无所惧。实盛世之美事。亟 还南铣以下宪府诸臣削职及赵锡胤罢职之 命。使群下咸知 圣上察理从善之美出寻常万万。而自此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2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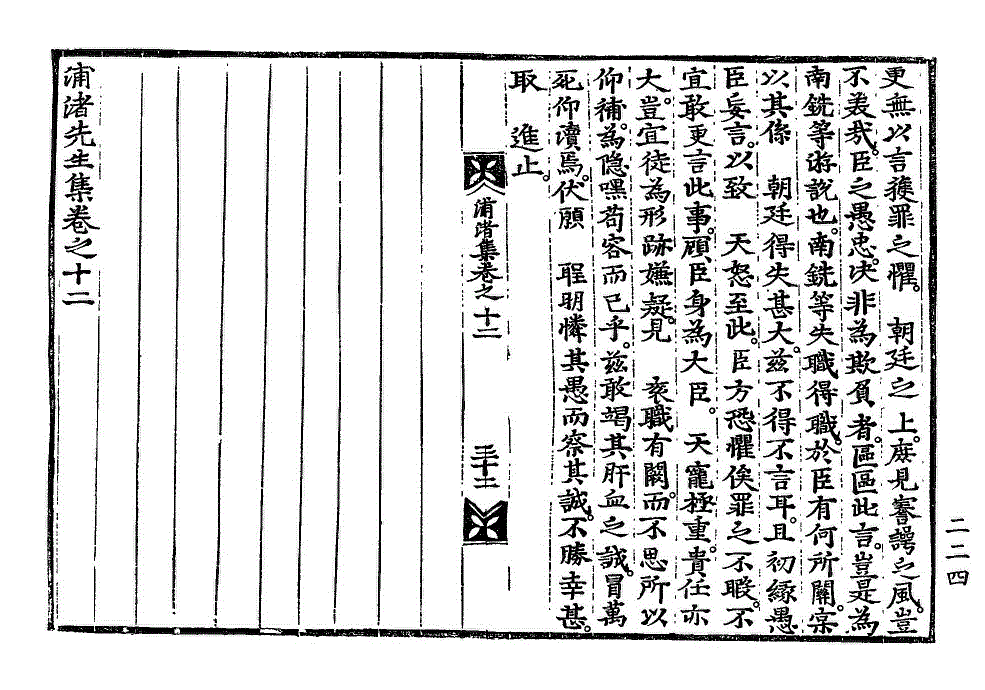 更无以言获罪之惧。 朝廷之上。庶见謇谔之风。岂不美哉。臣之愚忠。决非为欺负者。区区此言。岂是为南铣等游说也。南铣等失职得职。于臣有何所关。实以其系 朝廷得失甚大。兹不得不言耳。且初缘愚臣妄言。以致 天怒至此。臣方恐惧俟罪之不暇。不宜敢更言此事。顾臣身为大臣。 天宠极重。贵任亦大。岂宜徒为形迹嫌疑。见 衮职有阙。而不思所以仰补。为隐嘿苟容而已乎。兹敢竭其肝血之诚。冒万死仰渎焉。伏愿 圣明怜其愚而察其诚。不胜幸甚。取 进止。
更无以言获罪之惧。 朝廷之上。庶见謇谔之风。岂不美哉。臣之愚忠。决非为欺负者。区区此言。岂是为南铣等游说也。南铣等失职得职。于臣有何所关。实以其系 朝廷得失甚大。兹不得不言耳。且初缘愚臣妄言。以致 天怒至此。臣方恐惧俟罪之不暇。不宜敢更言此事。顾臣身为大臣。 天宠极重。贵任亦大。岂宜徒为形迹嫌疑。见 衮职有阙。而不思所以仰补。为隐嘿苟容而已乎。兹敢竭其肝血之诚。冒万死仰渎焉。伏愿 圣明怜其愚而察其诚。不胜幸甚。取 进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