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x 页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劄(八首)
劄(八首)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1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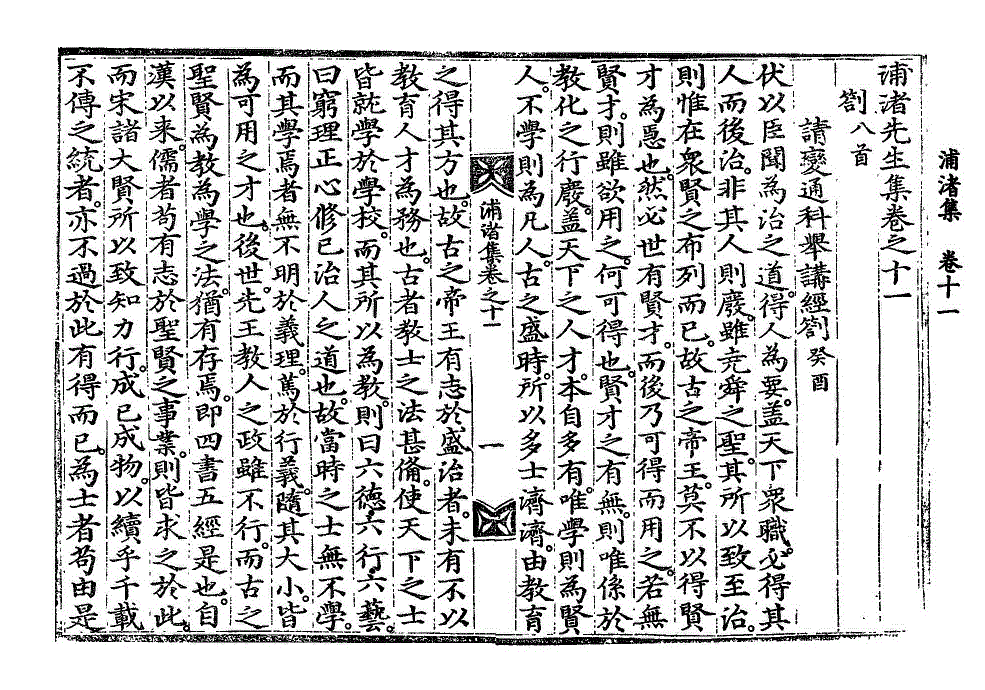 请变通科举讲经劄(癸酉)
请变通科举讲经劄(癸酉)伏以臣闻为治之道。得人为要。盖天下众职。必得其人而后治。非其人则废。虽尧舜之圣。其所以致至治。则惟在众贤之布列而已。故古之帝王。莫不以得贤才为急也。然必世有贤才。而后乃可得而用之。若无贤才。则虽欲用之。何可得也。贤才之有无。则唯系于教化之行废。盖天下之人才。本自多有。唯学则为贤人。不学则为凡人。古之盛时。所以多士济济。由教育之得其方也。故古之帝王有志于盛治者。未有不以教育人才为务也。古者教士之法甚备。使天下之士皆就学于学校。而其所以为教。则曰六德,六行,六艺。曰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也。故当时之士无不学。而其学焉者无不明于义理。笃于行义。随其大小。皆为可用之才也。后世。先王教人之政虽不行。而古之圣贤为教为学之法。犹有存焉。即四书五经是也。自汉以来。儒者苟有志于圣贤之事业。则皆求之于此。而宋诸大贤所以致知力行。成己成物。以续乎千载不传之统者。亦不过于此有得而已。为士者苟由是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1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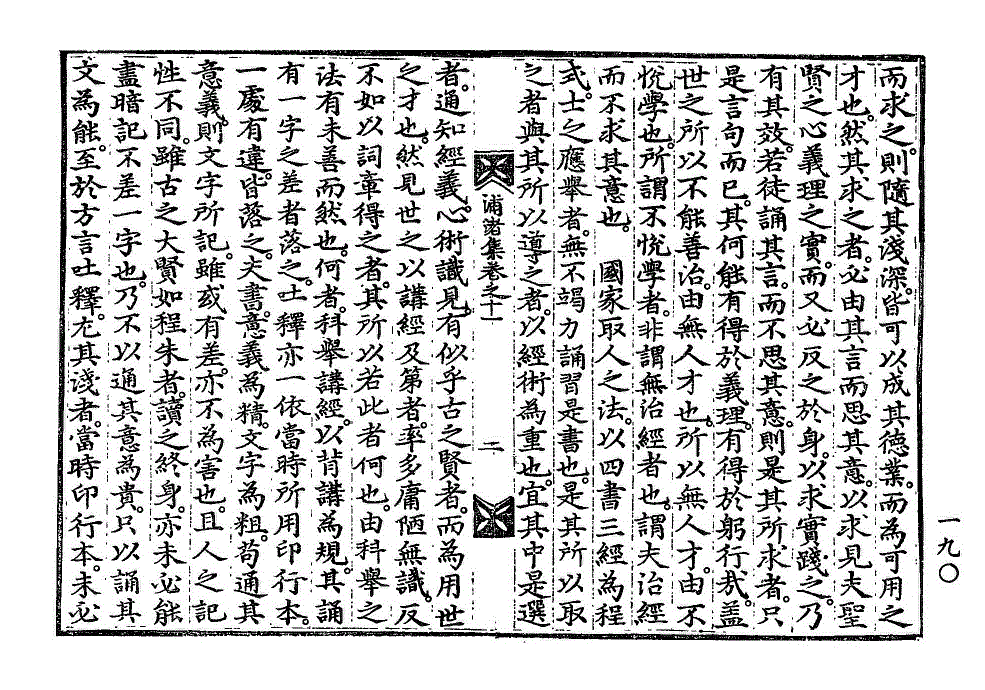 而求之。则随其浅深。皆可以成其德业。而为可用之才也。然其求之者。必由其言而思其意。以求见夫圣贤之心义理之实。而又必反之于身。以求实践之。乃有其效。若徒诵其言。而不思其意。则是其所求者。只是言句而已。其何能有得于义理。有得于躬行哉。盖世之所以不能善治。由无人才也。所以无人才。由不悦学也。所谓不悦学者。非谓无治经者也。谓夫治经而不求其意也。 国家取人之法。以四书三经为程式。士之应举者。无不竭力诵习是书也。是其所以取之者与其所以导之者。以经术为重也。宜其中是选者。通知经义。心术识见。有似乎古之贤者。而为用世之才也。然见世之以讲经及第者。率多庸陋无识。反不如以词章得之者。其所以若此者何也。由科举之法有未善而然也。何者。科举讲经。以背讲为规。其诵有一字之差者落之。吐释亦一依当时所用印行本。一处有违。皆落之。夫书。意义为精。文字为粗。苟通其意义。则文字所记。虽或有差。亦不为害也。且人之记性不同。虽古之大贤如程朱者。读之终身。亦未必能尽暗记不差一字也。乃不以通其意为贵。只以诵其文为能。至于方言吐释。尤其浅者。当时印行本。未必
而求之。则随其浅深。皆可以成其德业。而为可用之才也。然其求之者。必由其言而思其意。以求见夫圣贤之心义理之实。而又必反之于身。以求实践之。乃有其效。若徒诵其言。而不思其意。则是其所求者。只是言句而已。其何能有得于义理。有得于躬行哉。盖世之所以不能善治。由无人才也。所以无人才。由不悦学也。所谓不悦学者。非谓无治经者也。谓夫治经而不求其意也。 国家取人之法。以四书三经为程式。士之应举者。无不竭力诵习是书也。是其所以取之者与其所以导之者。以经术为重也。宜其中是选者。通知经义。心术识见。有似乎古之贤者。而为用世之才也。然见世之以讲经及第者。率多庸陋无识。反不如以词章得之者。其所以若此者何也。由科举之法有未善而然也。何者。科举讲经。以背讲为规。其诵有一字之差者落之。吐释亦一依当时所用印行本。一处有违。皆落之。夫书。意义为精。文字为粗。苟通其意义。则文字所记。虽或有差。亦不为害也。且人之记性不同。虽古之大贤如程朱者。读之终身。亦未必能尽暗记不差一字也。乃不以通其意为贵。只以诵其文为能。至于方言吐释。尤其浅者。当时印行本。未必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1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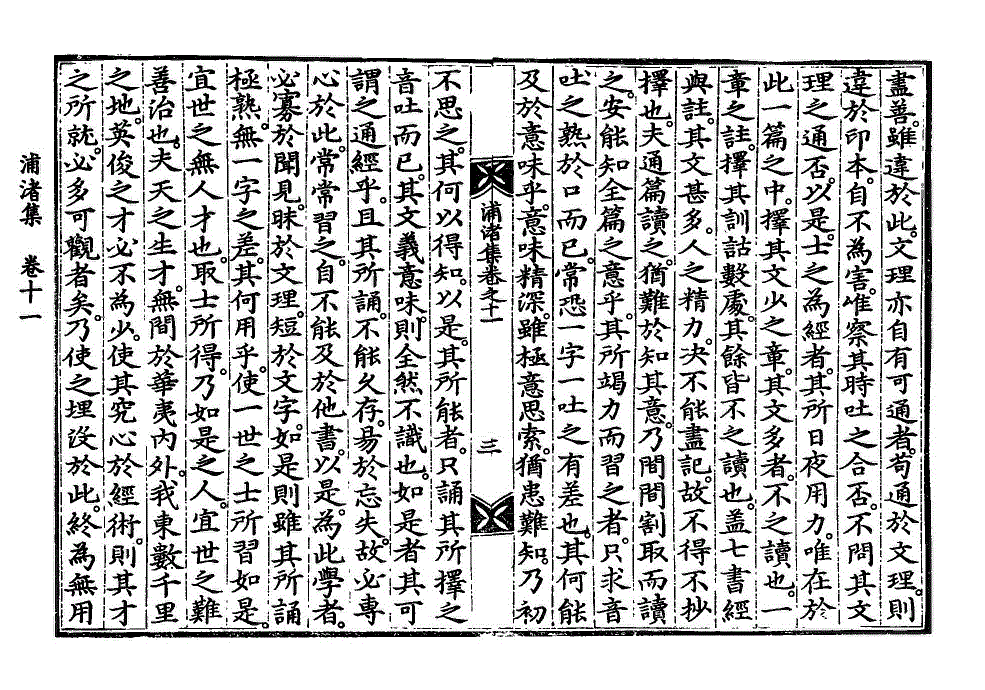 尽善。虽违于此。文理亦自有可通者。苟通于文理。则违于印本。自不为害。唯察其时吐之合否。不问其文理之通否。以是。士之为经者。其所日夜用力。唯在于此一篇之中。择其文少之章。其文多者。不之读也。一章之注。择其训诂数处。其馀皆不之读也。盖七书经与注。其文甚多。人之精力。决不能尽记。故不得不抄择也。夫通篇读之。犹难于知其意。乃间间割取而读之。安能知全篇之意乎。其所竭力而习之者。只求音吐之熟于口而已。常恐一字一吐之有差也。其何能及于意味乎。意味精深。虽极意思索。犹患难知。乃初不思之。其何以得知。以是。其所能者。只诵其所择之音吐而已。其文义意味。则全然不识也。如是者其可谓之通经乎。且其所诵。不能久存。易于忘失。故必专心于此。常常习之。自不能及于他书。以是。为此学者。必寡于闻见。昧于文理。短于文字。如是则虽其所诵极熟。无一字之差。其何用乎。使一世之士所习如是。宜世之无人才也。取士所得。乃如是之人。宜世之难善治也。夫天之生才。无间于华夷内外。我东数千里之地。英俊之才必不为少。使其究心于经术。则其才之所就。必多可观者矣。乃使之埋没于此。终为无用
尽善。虽违于此。文理亦自有可通者。苟通于文理。则违于印本。自不为害。唯察其时吐之合否。不问其文理之通否。以是。士之为经者。其所日夜用力。唯在于此一篇之中。择其文少之章。其文多者。不之读也。一章之注。择其训诂数处。其馀皆不之读也。盖七书经与注。其文甚多。人之精力。决不能尽记。故不得不抄择也。夫通篇读之。犹难于知其意。乃间间割取而读之。安能知全篇之意乎。其所竭力而习之者。只求音吐之熟于口而已。常恐一字一吐之有差也。其何能及于意味乎。意味精深。虽极意思索。犹患难知。乃初不思之。其何以得知。以是。其所能者。只诵其所择之音吐而已。其文义意味。则全然不识也。如是者其可谓之通经乎。且其所诵。不能久存。易于忘失。故必专心于此。常常习之。自不能及于他书。以是。为此学者。必寡于闻见。昧于文理。短于文字。如是则虽其所诵极熟。无一字之差。其何用乎。使一世之士所习如是。宜世之无人才也。取士所得。乃如是之人。宜世之难善治也。夫天之生才。无间于华夷内外。我东数千里之地。英俊之才必不为少。使其究心于经术。则其才之所就。必多可观者矣。乃使之埋没于此。终为无用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1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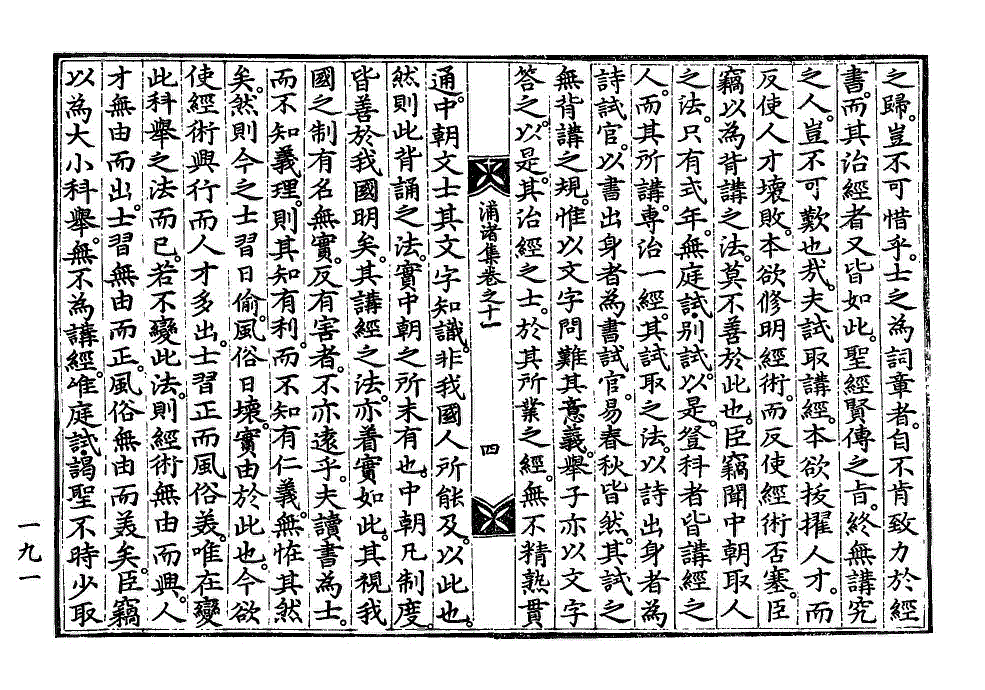 之归。岂不可惜乎。士之为词章者。自不肯致力于经书。而其治经者又皆如此。圣经贤传之旨。终无讲究之人。岂不可叹也哉。夫试取讲经。本欲拔擢人才。而反使人才坏败。本欲修明经术。而反使经术否塞。臣窃以为背讲之法。莫不善于此也。臣窃闻中朝取人之法。只有式年。无庭试,别试。以是。登科者皆讲经之人。而其所讲。专治一经。其试取之法。以诗出身者为诗试官。以书出身者为书试官。易春秋皆然。其试之无背讲之规。惟以文字问难其意义。举子亦以文字答之。以是。其治经之士。于其所业之经。无不精熟贯通。中朝文士其文字知识。非我国人所能及。以此也。然则此背诵之法。实中朝之所未有也。中朝凡制度。皆善于我国明矣。其讲经之法。亦着实如此。其视我国之制有名无实。反有害者。不亦远乎。夫读书为士。而不知义理。则其知有利。而不知有仁义。无怪其然矣。然则今之士习日偷。风俗日坏。实由于此也。今欲使经术兴行而人才多出。士习正而风俗美。唯在变此科举之法而已。若不变此法。则经术无由而兴。人才无由而出。士习无由而正。风俗无由而美矣。臣窃以为大小科举。无不为讲经。唯庭试,谒圣不时少取
之归。岂不可惜乎。士之为词章者。自不肯致力于经书。而其治经者又皆如此。圣经贤传之旨。终无讲究之人。岂不可叹也哉。夫试取讲经。本欲拔擢人才。而反使人才坏败。本欲修明经术。而反使经术否塞。臣窃以为背讲之法。莫不善于此也。臣窃闻中朝取人之法。只有式年。无庭试,别试。以是。登科者皆讲经之人。而其所讲。专治一经。其试取之法。以诗出身者为诗试官。以书出身者为书试官。易春秋皆然。其试之无背讲之规。惟以文字问难其意义。举子亦以文字答之。以是。其治经之士。于其所业之经。无不精熟贯通。中朝文士其文字知识。非我国人所能及。以此也。然则此背诵之法。实中朝之所未有也。中朝凡制度。皆善于我国明矣。其讲经之法。亦着实如此。其视我国之制有名无实。反有害者。不亦远乎。夫读书为士。而不知义理。则其知有利。而不知有仁义。无怪其然矣。然则今之士习日偷。风俗日坏。实由于此也。今欲使经术兴行而人才多出。士习正而风俗美。唯在变此科举之法而已。若不变此法。则经术无由而兴。人才无由而出。士习无由而正。风俗无由而美矣。臣窃以为大小科举。无不为讲经。唯庭试,谒圣不时少取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1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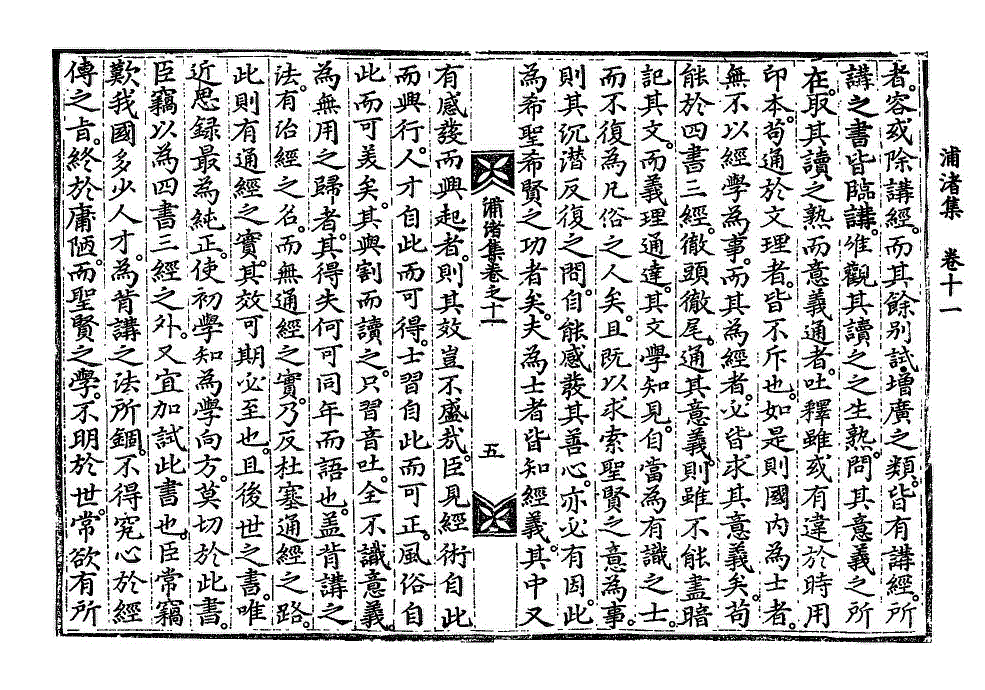 者。容或除讲经。而其馀别试,增广之类。皆有讲经。所讲之书皆临讲。唯观其读之之生熟。问其意义之所在。取其读之熟而意义通者。吐释虽或有违于时用印本。苟通于文理者。皆不斥也。如是则国内为士者。无不以经学为事。而其为经者。必皆求其意义矣。苟能于四书三经。彻头彻尾。通其意义。则虽不能尽暗记其文。而义理通达。其文学知见。自当为有识之士。而不复为凡俗之人矣。且既以求索圣贤之意为事。则其沈潜反复之间。自能感发其善心。亦必有因。此为希圣希贤之功者矣。夫为士者皆知经义。其中又有感发而兴起者。则其效岂不盛哉。臣见经术自此而兴行。人才自此而可得。士习自此而可正。风俗自此而可美矣。其与割而读之。只习音吐。全不识意义。为无用之归者。其得失何可同年而语也。盖背讲之法。有治经之名。而无通经之实。乃反杜塞通经之路。此则有通经之实。其效可期必至也。且后世之书。唯近思录最为纯正。使初学知为学向方。莫切于此书。臣窃以为四书三经之外。又宜加试此书也。臣常窃叹我国多少人才。为背讲之法所锢。不得究心于经传之旨。终于庸陋。而圣贤之学。不明于世。常欲有所
者。容或除讲经。而其馀别试,增广之类。皆有讲经。所讲之书皆临讲。唯观其读之之生熟。问其意义之所在。取其读之熟而意义通者。吐释虽或有违于时用印本。苟通于文理者。皆不斥也。如是则国内为士者。无不以经学为事。而其为经者。必皆求其意义矣。苟能于四书三经。彻头彻尾。通其意义。则虽不能尽暗记其文。而义理通达。其文学知见。自当为有识之士。而不复为凡俗之人矣。且既以求索圣贤之意为事。则其沈潜反复之间。自能感发其善心。亦必有因。此为希圣希贤之功者矣。夫为士者皆知经义。其中又有感发而兴起者。则其效岂不盛哉。臣见经术自此而兴行。人才自此而可得。士习自此而可正。风俗自此而可美矣。其与割而读之。只习音吐。全不识意义。为无用之归者。其得失何可同年而语也。盖背讲之法。有治经之名。而无通经之实。乃反杜塞通经之路。此则有通经之实。其效可期必至也。且后世之书。唯近思录最为纯正。使初学知为学向方。莫切于此书。臣窃以为四书三经之外。又宜加试此书也。臣常窃叹我国多少人才。为背讲之法所锢。不得究心于经传之旨。终于庸陋。而圣贤之学。不明于世。常欲有所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1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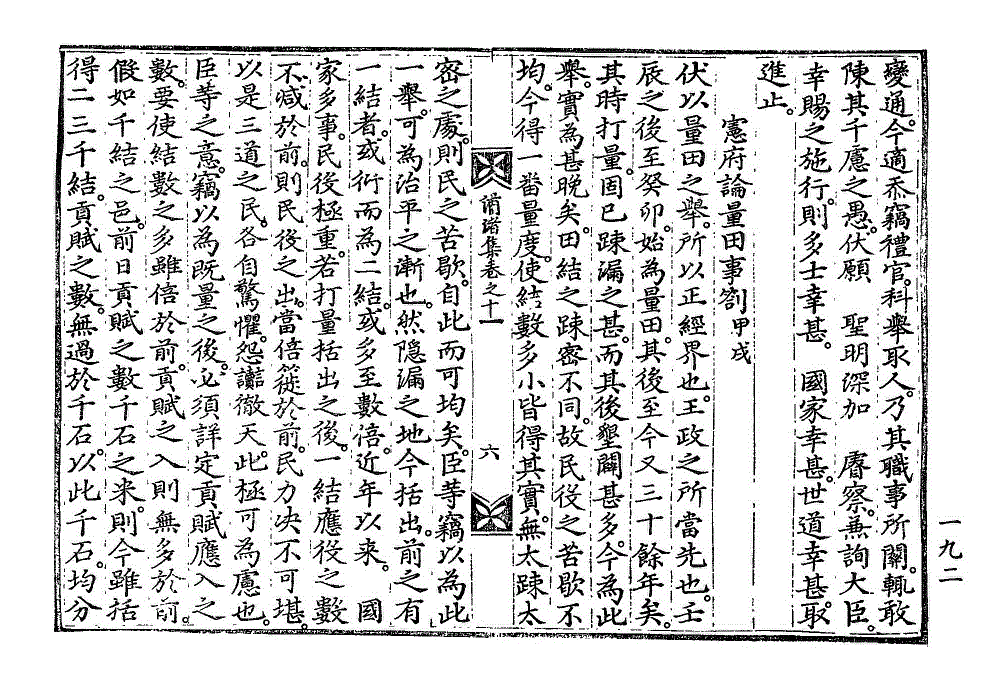 变通。今适忝窃礼官。科举取人。乃其职事所关。辄敢陈其千虑之愚。伏愿 圣明深加 睿察。兼询大臣。幸赐之施行。则多士幸甚。 国家幸甚。世道幸甚。取进止。
变通。今适忝窃礼官。科举取人。乃其职事所关。辄敢陈其千虑之愚。伏愿 圣明深加 睿察。兼询大臣。幸赐之施行。则多士幸甚。 国家幸甚。世道幸甚。取进止。宪府论量田事劄(甲戌)
伏以量田之举。所以正经界也。王政之所当先也。壬辰之后至癸卯。始为量田。其后至今又三十馀年矣。其时打量。固已疏漏之甚。而其后垦辟甚多。今为此举。实为甚晚矣。田结之疏密不同。故民役之苦歇不均。今得一番量度。使结数多小皆得其实。无太疏太密之处。则民之苦歇。自此而可均矣。臣等窃以为此一举。可为治平之渐也。然隐漏之地今括出。前之有一结者。或衍而为二结。或多至数倍。近年以来。 国家多事。民役极重。若打量括出之后。一结应役之数不减于前。则民役之出。当倍蓰于前。民力决不可堪。以是三道之民。各自惊惧。怨讟彻天。此极可为虑也。臣等之意。窃以为既量之后。必须详定贡赋应入之数。要使结数之多虽倍于前。贡赋之入则无多于前。假如千结之邑。前日贡赋之数千石之米。则今虽括得二三千结。贡赋之数。无过于千石。以此千石。均分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1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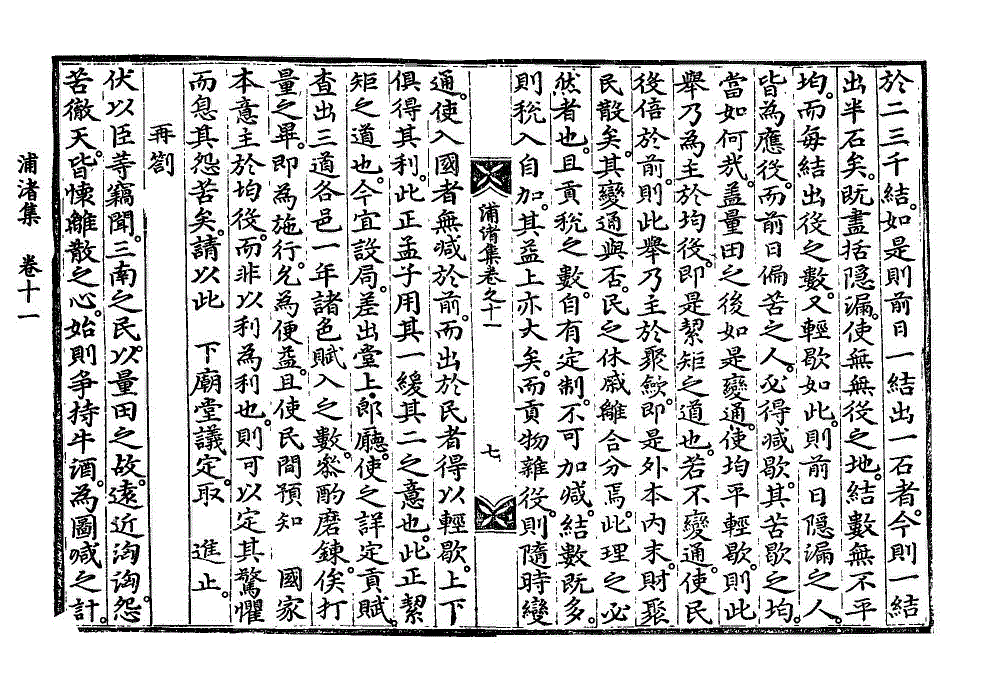 于二三千结。如是则前日一结出一石者。今则一结出半石矣。既尽括隐漏。使无无役之地。结数无不平均。而每结出役之数。又轻歇如此。则前日隐漏之人。皆为应役。而前日偏苦之人。必得减歇。其苦歇之均。当如何哉。盖量田之后如是变通。使均平轻歇。则此举乃为主于均役。即是絜矩之道也。若不变通。使民役倍于前。则此举乃主于聚敛。即是外本内末。财聚民散矣。其变通与否。民之休戚离合分焉。此理之必然者也。且贡税之数。自有定制。不可加减。结数既多。则税入自加。其益上亦大矣。而贡物杂役。则随时变通。使入国者无减于前。而出于民者得以轻歇。上下俱得其利。此正孟子用其一缓其二之意也。此正絜矩之道也。今宜设局。差出堂上,郎厅。使之详定贡赋。查出三道各邑一年诸色赋入之数。参酌磨鍊。俟打量之毕。即为施行。允为便益。且使民间预知 国家本意主于均役。而非以利为利也。则可以定其惊惧而息其怨苦矣。请以此 下庙堂议定。取 进止。
于二三千结。如是则前日一结出一石者。今则一结出半石矣。既尽括隐漏。使无无役之地。结数无不平均。而每结出役之数。又轻歇如此。则前日隐漏之人。皆为应役。而前日偏苦之人。必得减歇。其苦歇之均。当如何哉。盖量田之后如是变通。使均平轻歇。则此举乃为主于均役。即是絜矩之道也。若不变通。使民役倍于前。则此举乃主于聚敛。即是外本内末。财聚民散矣。其变通与否。民之休戚离合分焉。此理之必然者也。且贡税之数。自有定制。不可加减。结数既多。则税入自加。其益上亦大矣。而贡物杂役。则随时变通。使入国者无减于前。而出于民者得以轻歇。上下俱得其利。此正孟子用其一缓其二之意也。此正絜矩之道也。今宜设局。差出堂上,郎厅。使之详定贡赋。查出三道各邑一年诸色赋入之数。参酌磨鍊。俟打量之毕。即为施行。允为便益。且使民间预知 国家本意主于均役。而非以利为利也。则可以定其惊惧而息其怨苦矣。请以此 下庙堂议定。取 进止。宪府论量田事劄[再劄]
伏以臣等窃闻。三南之民。以量田之故。远近汹汹。怨苦彻天。皆怀离散之心。始则争持牛酒。为图减之计。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1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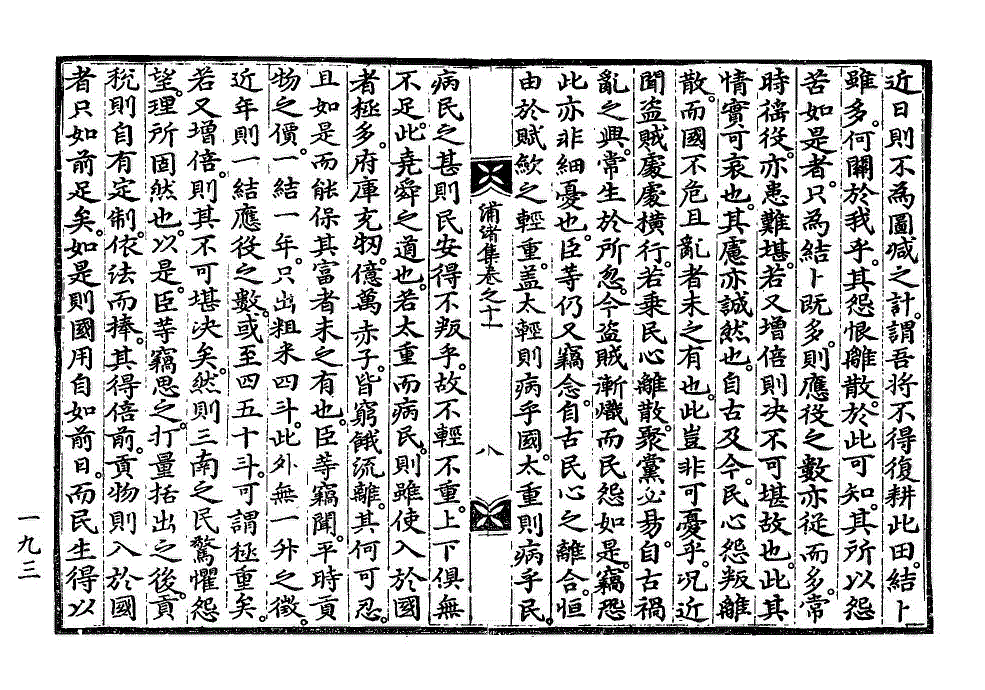 近日则不为图减之计。谓吾将不得复耕此田。结卜虽多。何关于我乎。其怨恨离散。于此可知。其所以怨苦如是者。只为结卜既多。则应役之数亦从而多。常时徭役。亦患难堪。若又增倍则决不可堪故也。此其情实可哀也。其虑亦诚然也。自古及今。民心怨叛离散。而国不危且乱者未之有也。此岂非可忧乎。况近闻盗贼处处横行。若乘民心离散。聚党必易。自古祸乱之兴。常生于所忽。今盗贼渐炽而民怨如是。窃恐此亦非细忧也。臣等仍又窃念。自古民心之离合。恒由于赋敛之轻重。盖太轻则病乎国。太重则病乎民。病民之甚则民安得不叛乎。故不轻不重。上下俱无不足。此尧舜之道也。若太重而病民。则虽使入于国者极多。府库充牣。亿万赤子。皆穷饿流离。其何可忍。且如是而能保其富者未之有也。臣等窃闻。平时贡物之价。一结一年。只出粗米四斗。此外无一升之徵。近年则一结应役之数。或至四五十斗。可谓极重矣。若又增倍。则其不可堪决矣。然则三南之民惊惧怨望。理所固然也。以是。臣等窃思之。打量括出之后。贡税则自有定制。依法而捧。其得倍前。贡物则入于国者只如前足矣。如是则国用自如前日。而民生得以
近日则不为图减之计。谓吾将不得复耕此田。结卜虽多。何关于我乎。其怨恨离散。于此可知。其所以怨苦如是者。只为结卜既多。则应役之数亦从而多。常时徭役。亦患难堪。若又增倍则决不可堪故也。此其情实可哀也。其虑亦诚然也。自古及今。民心怨叛离散。而国不危且乱者未之有也。此岂非可忧乎。况近闻盗贼处处横行。若乘民心离散。聚党必易。自古祸乱之兴。常生于所忽。今盗贼渐炽而民怨如是。窃恐此亦非细忧也。臣等仍又窃念。自古民心之离合。恒由于赋敛之轻重。盖太轻则病乎国。太重则病乎民。病民之甚则民安得不叛乎。故不轻不重。上下俱无不足。此尧舜之道也。若太重而病民。则虽使入于国者极多。府库充牣。亿万赤子。皆穷饿流离。其何可忍。且如是而能保其富者未之有也。臣等窃闻。平时贡物之价。一结一年。只出粗米四斗。此外无一升之徵。近年则一结应役之数。或至四五十斗。可谓极重矣。若又增倍。则其不可堪决矣。然则三南之民惊惧怨望。理所固然也。以是。臣等窃思之。打量括出之后。贡税则自有定制。依法而捧。其得倍前。贡物则入于国者只如前足矣。如是则国用自如前日。而民生得以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1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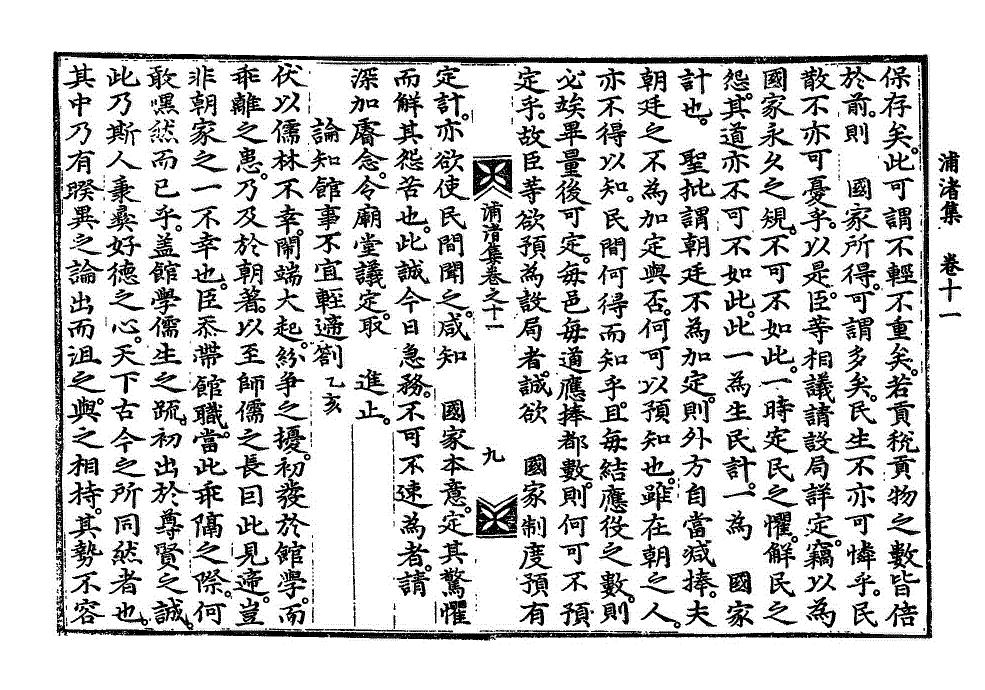 保存矣。此可谓不轻不重矣。若贡税贡物之数皆倍于前。则 国家所得。可谓多矣。民生不亦可怜乎。民散不亦可忧乎。以是。臣等相议请设局详定。窃以为国家永久之规。不可不如此。一时定民之惧。解民之恐。其道亦不可不如此。此一为生民计。一为 国家计也。 圣批谓朝廷不为加定。则外方自当减捧。夫朝廷之不为加定与否。何可以预知也。虽在朝之人。亦不得以知。民间何得而知乎。且每结应役之数。则必俟毕量后可定。每邑每道应捧都数。则何可不预定乎。故臣等欲预为设局者。诚欲 国家制度预有定计。亦欲使民间闻之。咸知 国家本意。定其惊惧而解其怨苦也。此诚今日急务。不可不速为者。请 深加睿念。令庙堂议定。取 进止。
保存矣。此可谓不轻不重矣。若贡税贡物之数皆倍于前。则 国家所得。可谓多矣。民生不亦可怜乎。民散不亦可忧乎。以是。臣等相议请设局详定。窃以为国家永久之规。不可不如此。一时定民之惧。解民之恐。其道亦不可不如此。此一为生民计。一为 国家计也。 圣批谓朝廷不为加定。则外方自当减捧。夫朝廷之不为加定与否。何可以预知也。虽在朝之人。亦不得以知。民间何得而知乎。且每结应役之数。则必俟毕量后可定。每邑每道应捧都数。则何可不预定乎。故臣等欲预为设局者。诚欲 国家制度预有定计。亦欲使民间闻之。咸知 国家本意。定其惊惧而解其怨苦也。此诚今日急务。不可不速为者。请 深加睿念。令庙堂议定。取 进止。论知馆事不宜轻递劄(乙亥)
伏以儒林不幸。闹端大起。纷争之扰。初发于馆学。而乖离之患。乃及于朝著。以至师儒之长因此见递。岂非朝家之一不幸也。臣忝带馆职。当此乖隔之际。何敢嘿然而已乎。盖馆学儒生之疏。初出于尊贤之诚。此乃斯人秉彝好德之心。天下古今之所同然者也。其中乃有暌异之论出而沮之。与之相持。其势不容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1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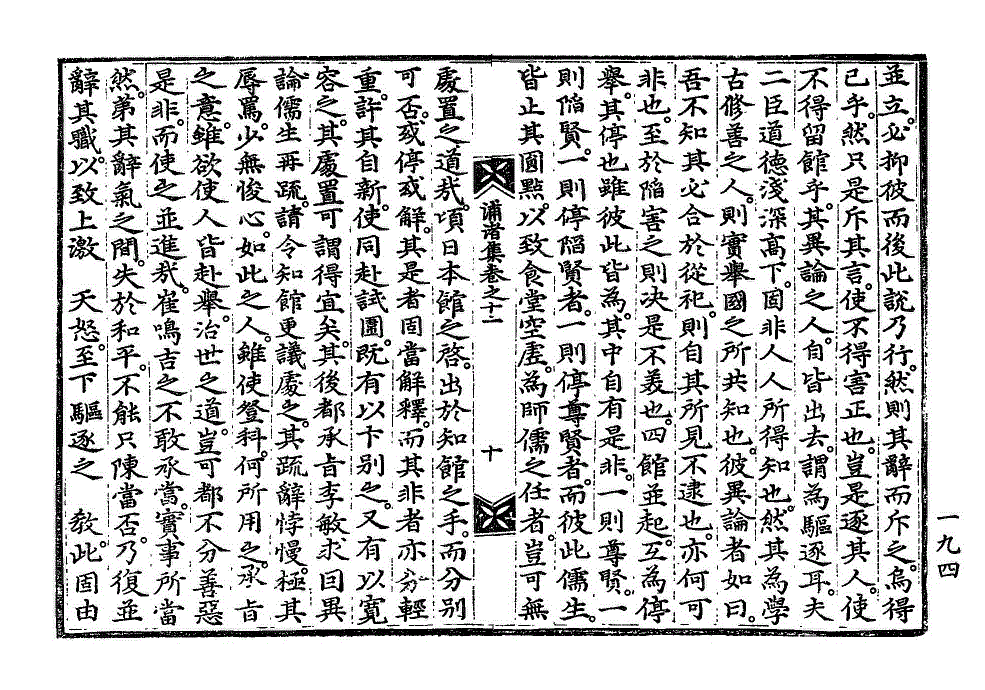 并立。必抑彼而后此说乃行。然则其辞而斥之。乌得已乎。然只是斥其言。使不得害正也。岂是逐其人。使不得留馆乎。其异论之人。自皆出去。谓为驱逐耳。夫二臣道德浅深高下。固非人人所得知也。然其为学古修善之人。则实举国之所共知也。彼异论者如曰。吾不知其必合于从祀。则自其所见不逮也。亦何可非也。至于陷害之则决是不美也。四馆并起。互为停举。其停也虽彼此皆为。其中自有是非。一则尊贤。一则陷贤。一则停陷贤者。一则停尊贤者。而彼此儒生。皆止其圆点。以致食堂空虚。为师儒之任者。岂可无处置之道哉。顷日本馆之启。出于知馆之手。而分别可否。或停或解。其是者固当解释。而其非者亦分轻重。许其自新。使同赴试围。既有以卞别之。又有以宽容之。其处置可谓得宜矣。其后都承旨李敏求因异论儒生再疏。请令知馆更议处之。其疏辞悖慢。极其辱骂。少无悛心。如此之人。虽使登科。何所用之。承旨之意。虽欲使人皆赴举。治世之道。岂可都不分善恶是非。而使之并进哉。崔鸣吉之不敢承当。实事所当然。第其辞气之间。失于和平。不能只陈当否。乃复并辞其职。以致上激 天怒。至下驱逐之 教。此固由
并立。必抑彼而后此说乃行。然则其辞而斥之。乌得已乎。然只是斥其言。使不得害正也。岂是逐其人。使不得留馆乎。其异论之人。自皆出去。谓为驱逐耳。夫二臣道德浅深高下。固非人人所得知也。然其为学古修善之人。则实举国之所共知也。彼异论者如曰。吾不知其必合于从祀。则自其所见不逮也。亦何可非也。至于陷害之则决是不美也。四馆并起。互为停举。其停也虽彼此皆为。其中自有是非。一则尊贤。一则陷贤。一则停陷贤者。一则停尊贤者。而彼此儒生。皆止其圆点。以致食堂空虚。为师儒之任者。岂可无处置之道哉。顷日本馆之启。出于知馆之手。而分别可否。或停或解。其是者固当解释。而其非者亦分轻重。许其自新。使同赴试围。既有以卞别之。又有以宽容之。其处置可谓得宜矣。其后都承旨李敏求因异论儒生再疏。请令知馆更议处之。其疏辞悖慢。极其辱骂。少无悛心。如此之人。虽使登科。何所用之。承旨之意。虽欲使人皆赴举。治世之道。岂可都不分善恶是非。而使之并进哉。崔鸣吉之不敢承当。实事所当然。第其辞气之间。失于和平。不能只陈当否。乃复并辞其职。以致上激 天怒。至下驱逐之 教。此固由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195H 页
 鸣吉褊心之失。而窃恐 圣教亦未能深服儒生之心也。夫其志唯在尊贤。则其欲行之。岂可非也。非是欲行己志也。乃欲尊贤之道行也。既欲尊贤之道行。则异论之为害者。安得不斥之也。此亦非驱逐多士也。乃斥其害于尊贤者也。恐不可以此为儒生之罪也。儒生恐惧。不敢居馆。固其所也。而太学之空。亦一时之异事也。鸣吉以由己而致此。其安敢自安于心。而不为之辞乎。而 殿下遽命递之。夫鸣吉前后处置。皆非有失也。其所失只是辞语之间。愠承旨之议。不能平其心耳。而其任主一时之文事。长儒林之师席。岂不重哉。今乃以一小失而遽递之。窃恐 殿下处重任。未免为太轻也。臣忝冒儒馆。当初处置。实与同之。其后展转至此。窃不胜惭惶震恐。敢陈区区所怀。伏冀 圣明之垂察焉。取 进止。
鸣吉褊心之失。而窃恐 圣教亦未能深服儒生之心也。夫其志唯在尊贤。则其欲行之。岂可非也。非是欲行己志也。乃欲尊贤之道行也。既欲尊贤之道行。则异论之为害者。安得不斥之也。此亦非驱逐多士也。乃斥其害于尊贤者也。恐不可以此为儒生之罪也。儒生恐惧。不敢居馆。固其所也。而太学之空。亦一时之异事也。鸣吉以由己而致此。其安敢自安于心。而不为之辞乎。而 殿下遽命递之。夫鸣吉前后处置。皆非有失也。其所失只是辞语之间。愠承旨之议。不能平其心耳。而其任主一时之文事。长儒林之师席。岂不重哉。今乃以一小失而遽递之。窃恐 殿下处重任。未免为太轻也。臣忝冒儒馆。当初处置。实与同之。其后展转至此。窃不胜惭惶震恐。敢陈区区所怀。伏冀 圣明之垂察焉。取 进止。论沈阳送使劄(丙子)
伏以今者信使之遣。 庙议已定。发行且有日。而谏院,玉堂。交章请停。夫 庙堂三司皆是为 国家计。而所见之不合如是。此今日国论之难决者也。夫天下之事。只有可与否而已。处之之道。唯当察于可否。而决其取舍。不可执一论也。今待虏之道。亦当察其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1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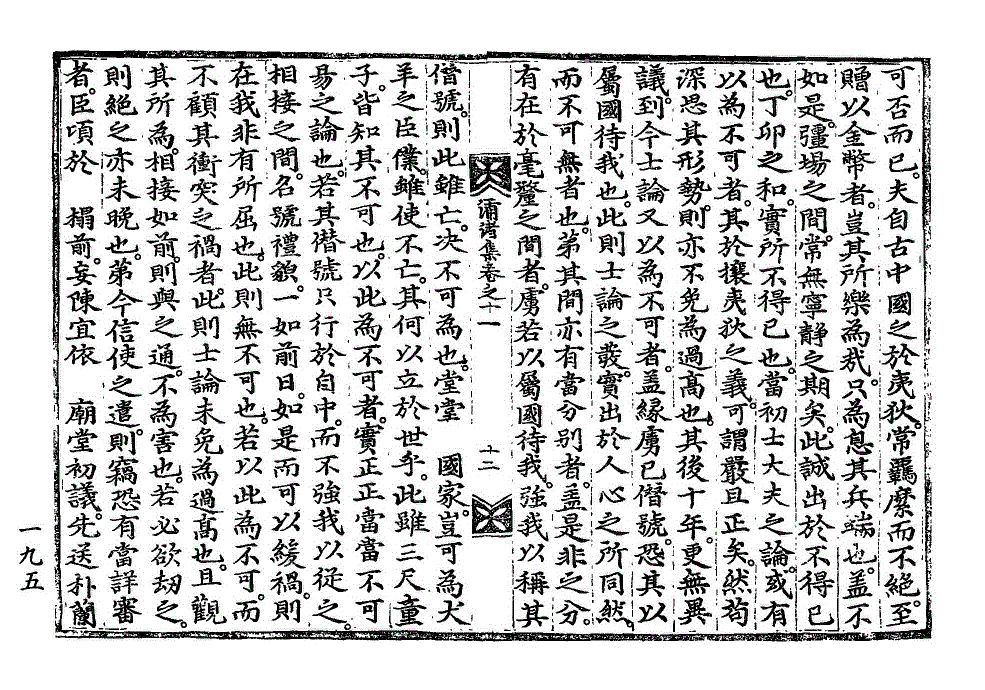 可否而已。夫自古中国之于夷狄。常羁縻而不绝。至赠以金币者。岂其所乐为哉。只为息其兵端也。盖不如是。疆埸之间。常无宁静之期矣。此诚出于不得已也。丁卯之和。实所不得已也。当初士大夫之论。或有以为不可者。其于攘夷狄之义。可谓严且正矣。然苟深思其形势。则亦不免为过高也。其后十年。更无异议。到今士论又以为不可者。盖缘虏已僭号。恐其以属国待我也。此则士论之发。实出于人心之所同然。而不可无者也。第其间亦有当分别者。盖是非之分。有在于毫釐之间者。虏若以属国待我。强我以称其僭号。则此虽亡。决不可为也。堂堂 国家。岂可为犬羊之臣仆。虽使不亡。其何以立于世乎。此虽三尺童子。皆知其不可也。以此为不可者。实正正当当不可易之论也。若其僭号只行于自中。而不强我以从之。相接之间。名号礼貌。一如前日。如是而可以缓祸。则在我非有所屈也。此则无不可也。若以此为不可。而不顾其冲突之祸者。此则士论未免为过高也。且观其所为。相接如前。则与之通。不为害也。若必欲劫之。则绝之亦未晚也。第今信使之遣。则窃恐有当详审者。臣顷于 榻前。妄陈宜依 庙堂初议。先送朴兰
可否而已。夫自古中国之于夷狄。常羁縻而不绝。至赠以金币者。岂其所乐为哉。只为息其兵端也。盖不如是。疆埸之间。常无宁静之期矣。此诚出于不得已也。丁卯之和。实所不得已也。当初士大夫之论。或有以为不可者。其于攘夷狄之义。可谓严且正矣。然苟深思其形势。则亦不免为过高也。其后十年。更无异议。到今士论又以为不可者。盖缘虏已僭号。恐其以属国待我也。此则士论之发。实出于人心之所同然。而不可无者也。第其间亦有当分别者。盖是非之分。有在于毫釐之间者。虏若以属国待我。强我以称其僭号。则此虽亡。决不可为也。堂堂 国家。岂可为犬羊之臣仆。虽使不亡。其何以立于世乎。此虽三尺童子。皆知其不可也。以此为不可者。实正正当当不可易之论也。若其僭号只行于自中。而不强我以从之。相接之间。名号礼貌。一如前日。如是而可以缓祸。则在我非有所屈也。此则无不可也。若以此为不可。而不顾其冲突之祸者。此则士论未免为过高也。且观其所为。相接如前。则与之通。不为害也。若必欲劫之。则绝之亦未晚也。第今信使之遣。则窃恐有当详审者。臣顷于 榻前。妄陈宜依 庙堂初议。先送朴兰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196H 页
 英矣。臣言不见用。而 庙议以信使为定。臣反覆思量。终未能释然于心也。盖虏人之情。见我有畏惧之意。则便生骄气。我待之稍严。则不敢肆其陵轹。此其常态也。自今春以来。我之待虏。异于前日。八月。马胡来龙湾给货价。所以观我之意也。顷日小译之往。虏虽有恐动之言。显有喜其来之意。以是推之。则其不欲相绝。甚于我之不欲绝也。盖既于大邦为雠。又与我为雠。则敌多而力分。有害而无利。故为虏计。其必不欲绝我明矣。虏情既如是。则虽与之和。当使操纵在我。今闻其虚喝之言。即送例信。如恐不及。则彼必以我为惧。便生轻侮之意。其劫之以难从之事。何惮而不为。故臣之愚意。宜先遣朴兰英。称以别使。谕以前者李廓等见辱。故不得送信使。今若相待如前。则何为绝邻好。因与讲定文书。称号必使无加于前。然后送信使。如是则虏知我之不可屈。不敢过有所求。而于我无所损伤矣。夫虏意诚不欲绝我。则虽送别使。与之讲定。必不为怒。如或不难于绝我。必欲劫我而从其僭号。则虽送信使。亦必以不尽从其意为怒也。然则其怒与不怒。不在于信使与别使也。而我之通信。则必先讲定而后乃可。今不先讲定。而遽送信
英矣。臣言不见用。而 庙议以信使为定。臣反覆思量。终未能释然于心也。盖虏人之情。见我有畏惧之意。则便生骄气。我待之稍严。则不敢肆其陵轹。此其常态也。自今春以来。我之待虏。异于前日。八月。马胡来龙湾给货价。所以观我之意也。顷日小译之往。虏虽有恐动之言。显有喜其来之意。以是推之。则其不欲相绝。甚于我之不欲绝也。盖既于大邦为雠。又与我为雠。则敌多而力分。有害而无利。故为虏计。其必不欲绝我明矣。虏情既如是。则虽与之和。当使操纵在我。今闻其虚喝之言。即送例信。如恐不及。则彼必以我为惧。便生轻侮之意。其劫之以难从之事。何惮而不为。故臣之愚意。宜先遣朴兰英。称以别使。谕以前者李廓等见辱。故不得送信使。今若相待如前。则何为绝邻好。因与讲定文书。称号必使无加于前。然后送信使。如是则虏知我之不可屈。不敢过有所求。而于我无所损伤矣。夫虏意诚不欲绝我。则虽送别使。与之讲定。必不为怒。如或不难于绝我。必欲劫我而从其僭号。则虽送信使。亦必以不尽从其意为怒也。然则其怒与不怒。不在于信使与别使也。而我之通信。则必先讲定而后乃可。今不先讲定。而遽送信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1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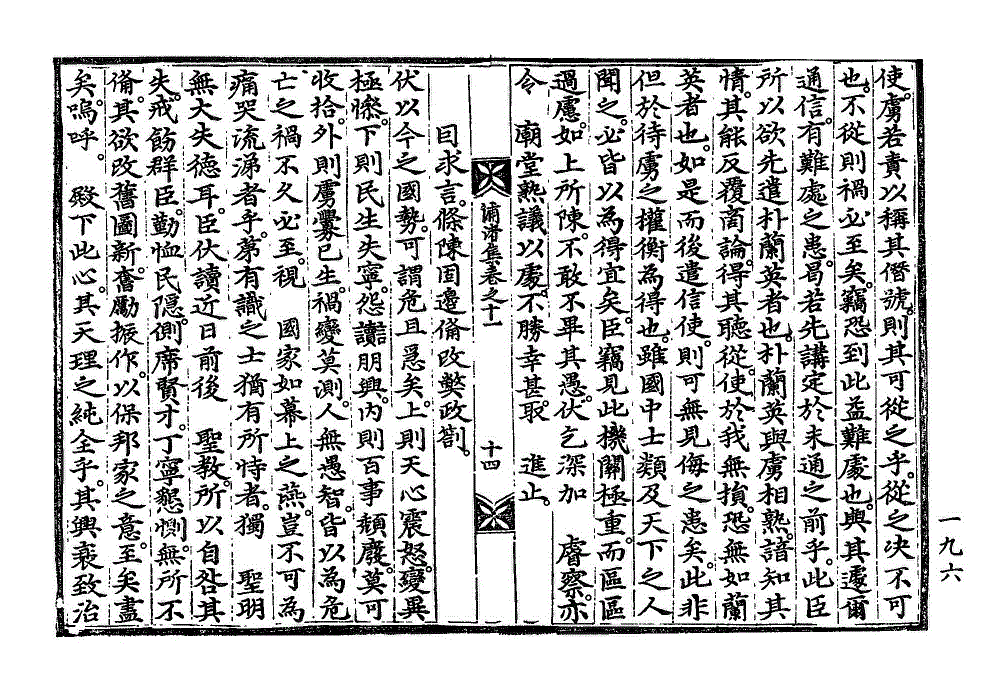 使。虏若责以称其僭号。则其可从之乎。从之决不可也。不从则祸必至矣。窃恐到此益难处也。与其遽尔通信。有难处之患。曷若先讲定于未通之前乎。此臣所以欲先遣朴兰英者也。朴兰英与虏相熟。谙知其情。其能反覆商论。得其听从。使于我无损。恐无如兰英者也。如是而后遣信使。则可无见侮之患矣。此非但于待虏之权衡为得也。虽国中士类及天下之人闻之。必皆以为得宜矣。臣窃见此机关极重。而区区过虑。如上所陈。不敢不毕其愚。伏乞深加 睿察。亦令 庙堂熟议以处。不胜幸甚。取 进止。
使。虏若责以称其僭号。则其可从之乎。从之决不可也。不从则祸必至矣。窃恐到此益难处也。与其遽尔通信。有难处之患。曷若先讲定于未通之前乎。此臣所以欲先遣朴兰英者也。朴兰英与虏相熟。谙知其情。其能反覆商论。得其听从。使于我无损。恐无如兰英者也。如是而后遣信使。则可无见侮之患矣。此非但于待虏之权衡为得也。虽国中士类及天下之人闻之。必皆以为得宜矣。臣窃见此机关极重。而区区过虑。如上所陈。不敢不毕其愚。伏乞深加 睿察。亦令 庙堂熟议以处。不胜幸甚。取 进止。因求言。条陈固边备改弊政劄。
伏以今之国势。可谓危且急矣。上则天心震怒。变异极惨。下则民生失宁。怨讟朋兴。内则百事颓废。莫可收拾。外则虏衅已生。祸变莫测。人无愚智。皆以为危亡之祸不久必至。视 国家如幕上之燕。岂不可为痛哭流涕者乎。第有识之士犹有所恃者。独 圣明无大失德耳。臣伏读近日前后 圣教。所以自咎其失。戒饬群臣。勤恤民隐。侧席贤才。丁宁恳恻。无所不备。其欲改旧图新。奋励振作。以保邦家之意。至矣尽矣。呜呼。 殿下此心。其天理之纯全乎。其兴衰致治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1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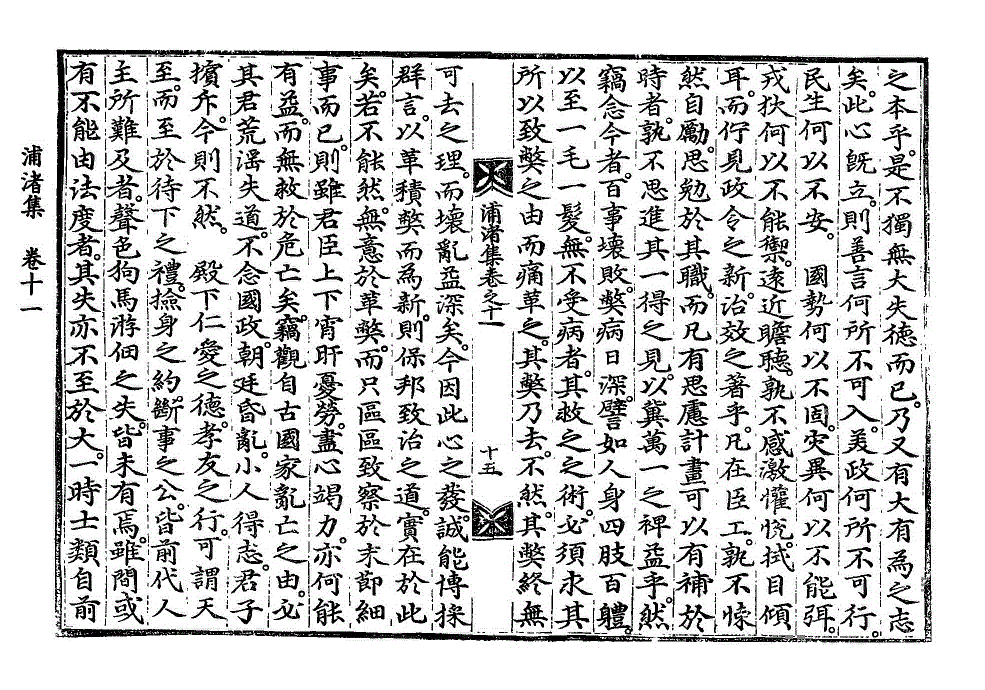 之本乎。是不独无大失德而已。乃又有大有为之志矣。此心既立。则善言何所不可入。美政何所不可行。民生何以不安。 国势何以不固。灾异何以不能弭。戎狄何以不能御。远近瞻听。孰不感激欢悦。拭目倾耳。而伫见政令之新。治效之著乎。凡在臣工。孰不悚然自励。思勉于其职。而凡有思虑计画可以有补于时者。孰不思进其一得之见。以冀万一之裨益乎。然窃念今者。百事坏败。弊病日深。譬如人身四肢百体。以至一毛一发。无不受病者。其救之之术。必须求其所以致弊之由而痛革之。其弊乃去。不然。其弊终无可去之理。而坏乱益深矣。今因此心之发。诚能博采群言。以革积弊而为新。则保邦致治之道。实在于此矣。若不能然。无意于革弊。而只区区致察于末节细事而已。则虽君臣上下宵旰忧劳。尽心竭力。亦何能有益。而无救于危亡矣。窃观自古国家乱亡之由。必其君荒淫失道。不念国政。朝廷昏乱。小人得志。君子摈斥。今则不然。 殿下仁爱之德。孝友之行。可谓天至。而至于待下之礼。检身之约。断事之公。皆前代人主所难及者。声色狗马游佃之失。皆未有焉。虽间或有不能由法度者。其失亦不至于大。一时士类自前
之本乎。是不独无大失德而已。乃又有大有为之志矣。此心既立。则善言何所不可入。美政何所不可行。民生何以不安。 国势何以不固。灾异何以不能弭。戎狄何以不能御。远近瞻听。孰不感激欢悦。拭目倾耳。而伫见政令之新。治效之著乎。凡在臣工。孰不悚然自励。思勉于其职。而凡有思虑计画可以有补于时者。孰不思进其一得之见。以冀万一之裨益乎。然窃念今者。百事坏败。弊病日深。譬如人身四肢百体。以至一毛一发。无不受病者。其救之之术。必须求其所以致弊之由而痛革之。其弊乃去。不然。其弊终无可去之理。而坏乱益深矣。今因此心之发。诚能博采群言。以革积弊而为新。则保邦致治之道。实在于此矣。若不能然。无意于革弊。而只区区致察于末节细事而已。则虽君臣上下宵旰忧劳。尽心竭力。亦何能有益。而无救于危亡矣。窃观自古国家乱亡之由。必其君荒淫失道。不念国政。朝廷昏乱。小人得志。君子摈斥。今则不然。 殿下仁爱之德。孝友之行。可谓天至。而至于待下之礼。检身之约。断事之公。皆前代人主所难及者。声色狗马游佃之失。皆未有焉。虽间或有不能由法度者。其失亦不至于大。一时士类自前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1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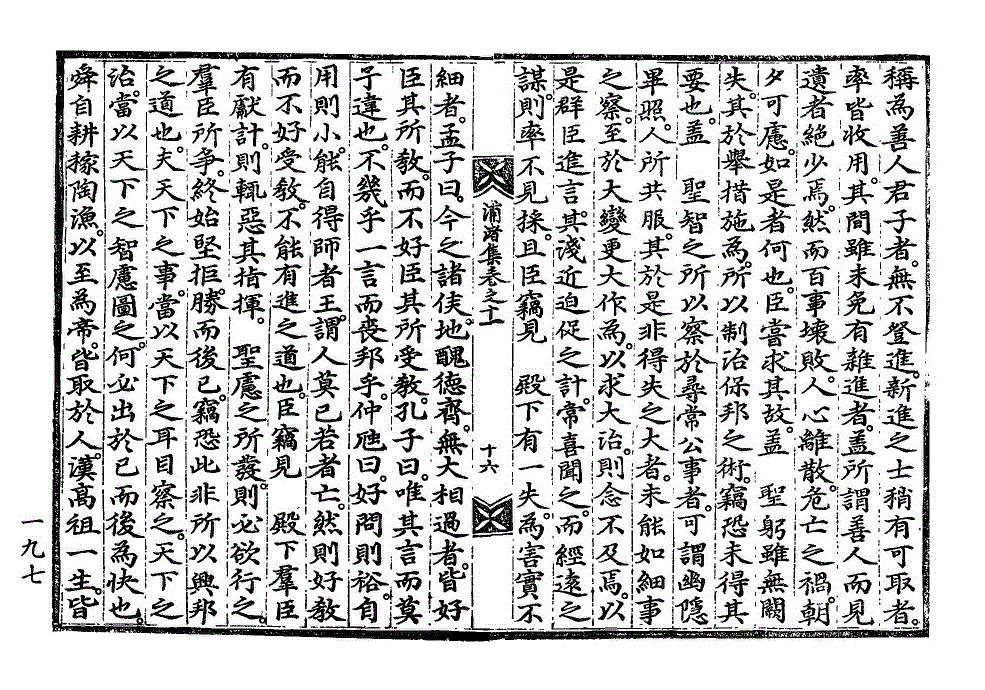 称为善人君子者。无不登进。新进之士稍有可取者。率皆收用。其间虽未免有杂进者。盖所谓善人而见遗者绝少焉。然而百事坏败。人心离散。危亡之祸。朝夕可虑。如是者何也。臣尝求其故。盖 圣躬虽无阙失。其于举措施为。所以制治保邦之术。窃恐未得其要也。盖 圣智之所以察于寻常公事者。可谓幽隐毕照。人所共服。其于是非得失之大者。未能如细事之察。至于大变更大作为。以求大治。则念不及焉。以是群臣进言。其浅近迫促之计。常喜闻之。而经远之谋。则率不见采。且臣窃见 殿下有一失。为害实不细者。孟子曰。今之诸侯。地丑德齐。无大相过者。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孔子曰。唯其言而莫予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仲虺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然则好教而不好受教。不能有进之道也。臣窃见 殿下群臣有献计。则辄恶其指挥。 圣虑之所发。则必欲行之。群臣所争。终始坚拒。胜而后已。窃恐此非所以兴邦之道也。夫天下之事。当以天下之耳目察之。天下之治。当以天下之智虑图之。何必出于己而后为快也。舜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皆取于人。汉高祖一生。皆
称为善人君子者。无不登进。新进之士稍有可取者。率皆收用。其间虽未免有杂进者。盖所谓善人而见遗者绝少焉。然而百事坏败。人心离散。危亡之祸。朝夕可虑。如是者何也。臣尝求其故。盖 圣躬虽无阙失。其于举措施为。所以制治保邦之术。窃恐未得其要也。盖 圣智之所以察于寻常公事者。可谓幽隐毕照。人所共服。其于是非得失之大者。未能如细事之察。至于大变更大作为。以求大治。则念不及焉。以是群臣进言。其浅近迫促之计。常喜闻之。而经远之谋。则率不见采。且臣窃见 殿下有一失。为害实不细者。孟子曰。今之诸侯。地丑德齐。无大相过者。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孔子曰。唯其言而莫予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仲虺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然则好教而不好受教。不能有进之道也。臣窃见 殿下群臣有献计。则辄恶其指挥。 圣虑之所发。则必欲行之。群臣所争。终始坚拒。胜而后已。窃恐此非所以兴邦之道也。夫天下之事。当以天下之耳目察之。天下之治。当以天下之智虑图之。何必出于己而后为快也。舜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皆取于人。汉高祖一生。皆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1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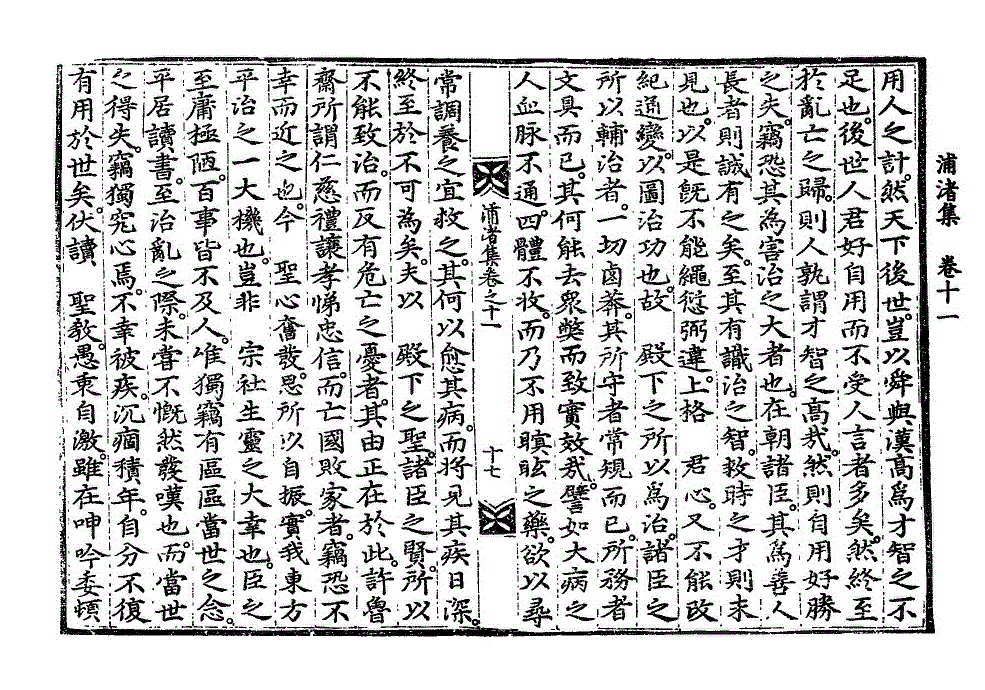 用人之计。然天下后世。岂以舜与汉高为才智之不足也。后世人君好自用而不受人言者多矣。然终至于乱亡之归。则人孰谓才智之高哉。然则自用好胜之失。窃恐其为害治之大者也。在朝诸臣。其为善人长者则诚有之矣。至其有识治之智。救时之才则未见也。以是既不能绳愆弼违。上格 君心。又不能改纪通变。以图治功也。故 殿下之所以为治。诸臣之所以辅治者。一切卤莽。其所守者常规而已。所务者文具而已。其何能去众弊而致实效哉。譬如大病之人血脉不通。四体不收。而乃不用瞑眩之药。欲以寻常调养之宜救之。其何以愈其病。而将见其疾日深。终至于不可为矣。夫以 殿下之圣。诸臣之贤。所以不能致治。而反有危亡之忧者。其由正在于此。许鲁斋所谓仁慈礼让孝悌忠信。而亡国败家者。窃恐不幸而近之也。今 圣心奋发。思所以自振。实我东方平治之一大机也。岂非 宗社生灵之大幸也。臣之至庸极陋。百事皆不及人。唯独窃有区区当世之念。平居读书。至治乱之际。未尝不慨然发叹也。而当世之得失。窃独究心焉。不幸被疾。沈痼积年。自分不复有用于世矣。伏读 圣教。愚衷自激。虽在呻吟委顿
用人之计。然天下后世。岂以舜与汉高为才智之不足也。后世人君好自用而不受人言者多矣。然终至于乱亡之归。则人孰谓才智之高哉。然则自用好胜之失。窃恐其为害治之大者也。在朝诸臣。其为善人长者则诚有之矣。至其有识治之智。救时之才则未见也。以是既不能绳愆弼违。上格 君心。又不能改纪通变。以图治功也。故 殿下之所以为治。诸臣之所以辅治者。一切卤莽。其所守者常规而已。所务者文具而已。其何能去众弊而致实效哉。譬如大病之人血脉不通。四体不收。而乃不用瞑眩之药。欲以寻常调养之宜救之。其何以愈其病。而将见其疾日深。终至于不可为矣。夫以 殿下之圣。诸臣之贤。所以不能致治。而反有危亡之忧者。其由正在于此。许鲁斋所谓仁慈礼让孝悌忠信。而亡国败家者。窃恐不幸而近之也。今 圣心奋发。思所以自振。实我东方平治之一大机也。岂非 宗社生灵之大幸也。臣之至庸极陋。百事皆不及人。唯独窃有区区当世之念。平居读书。至治乱之际。未尝不慨然发叹也。而当世之得失。窃独究心焉。不幸被疾。沈痼积年。自分不复有用于世矣。伏读 圣教。愚衷自激。虽在呻吟委顿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1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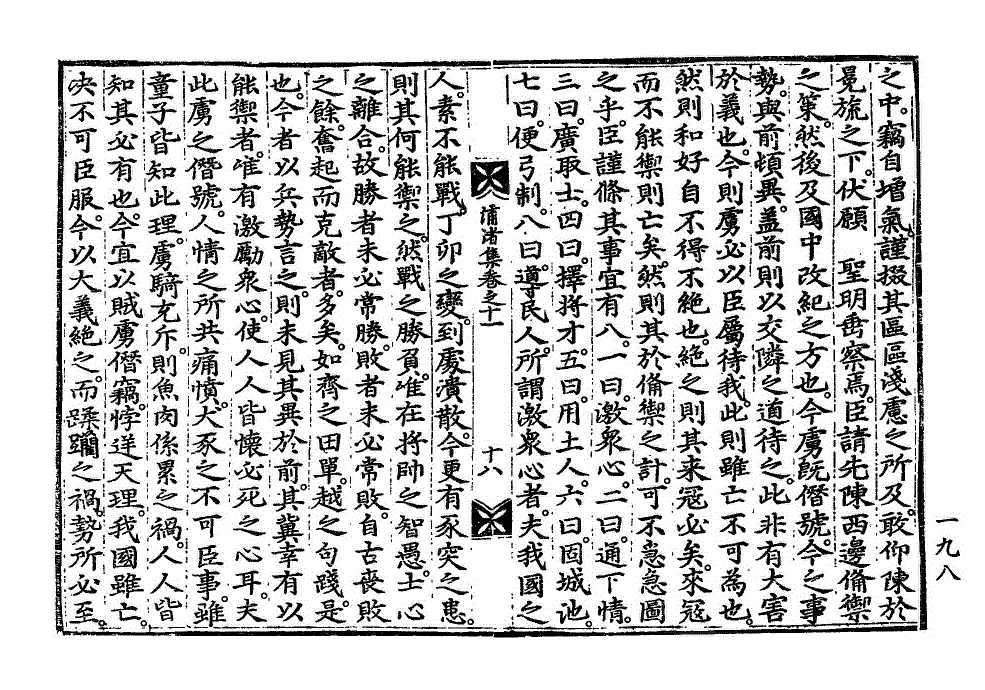 之中。窃自增气。谨掇其区区浅虑之所及。敢仰陈于冕旒之下。伏愿 圣明垂察焉。臣请先陈西边备御之策。然后及国中改纪之方也。今虏既僭号。今之事势。与前顿异。盖前则以交邻之道待之。此非有大害于义也。今则虏必以臣属待我。此则虽亡不可为也。然则和好自不得不绝也。绝之则其来寇必矣。来寇而不能御则亡矣。然则其于备御之计。可不急急图之乎。臣谨条其事宜有八。一曰。激众心。二曰。通下情。三曰。广取士。四曰。择将才。五曰。用土人。六曰。固城池。七曰。便弓制。八曰。导民人。所谓激众心者。夫我国之人。素不能战。丁卯之变。到处溃散。今更有豕突之患。则其何能御之。然战之胜负。唯在将帅之智愚。士心之离合。故胜者未必常胜。败者未必常败。自古丧败之馀。奋起而克敌者。多矣。如齐之田单。越之句践。是也。今者以兵势言之。则未见其异于前。其冀幸有以能御者。唯有激励众心。使人人皆怀必死之心耳。夫此虏之僭号。人情之所共痛愤。犬豕之不可臣事。虽童子皆知此理。虏骑充斥。则鱼肉系累之祸。人人皆知其必有也。今宜以贼虏僭窃。悖逆天理。我国虽亡。决不可臣服。今以大义绝之。而蹂躏之祸。势所必至。
之中。窃自增气。谨掇其区区浅虑之所及。敢仰陈于冕旒之下。伏愿 圣明垂察焉。臣请先陈西边备御之策。然后及国中改纪之方也。今虏既僭号。今之事势。与前顿异。盖前则以交邻之道待之。此非有大害于义也。今则虏必以臣属待我。此则虽亡不可为也。然则和好自不得不绝也。绝之则其来寇必矣。来寇而不能御则亡矣。然则其于备御之计。可不急急图之乎。臣谨条其事宜有八。一曰。激众心。二曰。通下情。三曰。广取士。四曰。择将才。五曰。用土人。六曰。固城池。七曰。便弓制。八曰。导民人。所谓激众心者。夫我国之人。素不能战。丁卯之变。到处溃散。今更有豕突之患。则其何能御之。然战之胜负。唯在将帅之智愚。士心之离合。故胜者未必常胜。败者未必常败。自古丧败之馀。奋起而克敌者。多矣。如齐之田单。越之句践。是也。今者以兵势言之。则未见其异于前。其冀幸有以能御者。唯有激励众心。使人人皆怀必死之心耳。夫此虏之僭号。人情之所共痛愤。犬豕之不可臣事。虽童子皆知此理。虏骑充斥。则鱼肉系累之祸。人人皆知其必有也。今宜以贼虏僭窃。悖逆天理。我国虽亡。决不可臣服。今以大义绝之。而蹂躏之祸。势所必至。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199H 页
 与其坐而待亡。曷若悉力御之。幸而能御。则 国家不亡。而生灵得以保全。虽或不幸而败死。犹胜臣服犬豕而偷生。为万世之羞耻也。且此虏技能。皆已知之。苟善为设计。竭力御之。则其胜不难矣。凡我将士军民。其各自淬厉。同力一意。遇贼进战。以必死为心也。虽退而走。贼若得志。则其终免于死乎。死一也。曷若战而死乎。以此意 下教。晓喻西路及八方之人。使深山穷谷皆得闻之。如是则军民之情。必皆感发鼓动。其气自倍。而不复如前日之解体矣。况西路之人。曾被其祸。痛入骨髓。人人以虏为雠。苟激励如是。则其感激振奋。皆怀死战之心必矣。所谓通下情者。夫天下之事。得失利害。其端无穷。智者或失之。而愚者或得之。在上者未必皆得。而在下者未必皆不得。古之圣人所以辟四门明四目。迩言必察。刍荛必询。常恐耳目有所不及。思虑有所不尽者。以此也。况当艰危之日。计策得失。成败立决。尤宜广其询访。使群策毕达也。臣窃闻 光庙朝。有李施爱之变。 光庙下令国中。凡有奇谋异策者。使皆来言。夫以 光庙之神谟睿策。乃复取于人如是。此亦岂非今之所当法乎。今此贼之患。实举国之所同害也。国内之人。如
与其坐而待亡。曷若悉力御之。幸而能御。则 国家不亡。而生灵得以保全。虽或不幸而败死。犹胜臣服犬豕而偷生。为万世之羞耻也。且此虏技能。皆已知之。苟善为设计。竭力御之。则其胜不难矣。凡我将士军民。其各自淬厉。同力一意。遇贼进战。以必死为心也。虽退而走。贼若得志。则其终免于死乎。死一也。曷若战而死乎。以此意 下教。晓喻西路及八方之人。使深山穷谷皆得闻之。如是则军民之情。必皆感发鼓动。其气自倍。而不复如前日之解体矣。况西路之人。曾被其祸。痛入骨髓。人人以虏为雠。苟激励如是。则其感激振奋。皆怀死战之心必矣。所谓通下情者。夫天下之事。得失利害。其端无穷。智者或失之。而愚者或得之。在上者未必皆得。而在下者未必皆不得。古之圣人所以辟四门明四目。迩言必察。刍荛必询。常恐耳目有所不及。思虑有所不尽者。以此也。况当艰危之日。计策得失。成败立决。尤宜广其询访。使群策毕达也。臣窃闻 光庙朝。有李施爱之变。 光庙下令国中。凡有奇谋异策者。使皆来言。夫以 光庙之神谟睿策。乃复取于人如是。此亦岂非今之所当法乎。今此贼之患。实举国之所同害也。国内之人。如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1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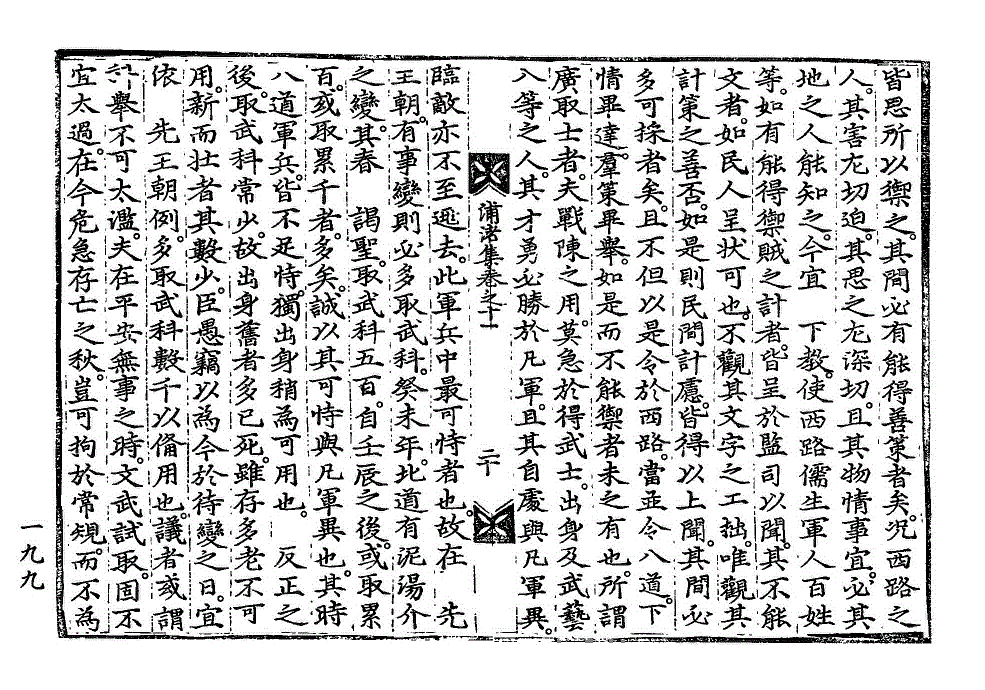 皆思所以御之。其间必有能得善策者矣。况西路之人。其害尤切迫。其思之尤深切。且其物情事宜。必其地之人能知之。今宜 下教。使西路儒生军人百姓等。如有能得御贼之计者。皆呈于监司以闻。其不能文者。如民人呈状可也。不观其文字之工拙。唯观其计策之善否。如是则民间计虑。皆得以上闻。其间必多可采者矣。且不但以是令于西路。当并令八道。下情毕达。群策毕举。如是而不能御者未之有也。所谓广取士者。夫战陈之用。莫急于得武士。出身及武艺入等之人。其才勇必胜于凡军。且其自处与凡军异。临敌亦不至逃去。此军兵中最可恃者也。故在 先王朝。有事变则必多取武科。癸未年。北道有泥汤介之变。其春 谒圣。取武科五百。自壬辰之后。或取累百。或取累千者。多矣。诚以其可恃与凡军异也。其时八道军兵。皆不足恃。独出身稍为可用也。 反正之后。取武科常少。故出身旧者多已死。虽存多老不可用。新而壮者其数少。臣愚窃以为今于待变之日。宜依 先王朝例。多取武科数千以备用也。议者或谓科举不可太滥。夫在平安无事之时。文武试取。固不宜太过。在今危急存亡之秋。岂可拘于常规。而不为
皆思所以御之。其间必有能得善策者矣。况西路之人。其害尤切迫。其思之尤深切。且其物情事宜。必其地之人能知之。今宜 下教。使西路儒生军人百姓等。如有能得御贼之计者。皆呈于监司以闻。其不能文者。如民人呈状可也。不观其文字之工拙。唯观其计策之善否。如是则民间计虑。皆得以上闻。其间必多可采者矣。且不但以是令于西路。当并令八道。下情毕达。群策毕举。如是而不能御者未之有也。所谓广取士者。夫战陈之用。莫急于得武士。出身及武艺入等之人。其才勇必胜于凡军。且其自处与凡军异。临敌亦不至逃去。此军兵中最可恃者也。故在 先王朝。有事变则必多取武科。癸未年。北道有泥汤介之变。其春 谒圣。取武科五百。自壬辰之后。或取累百。或取累千者。多矣。诚以其可恃与凡军异也。其时八道军兵。皆不足恃。独出身稍为可用也。 反正之后。取武科常少。故出身旧者多已死。虽存多老不可用。新而壮者其数少。臣愚窃以为今于待变之日。宜依 先王朝例。多取武科数千以备用也。议者或谓科举不可太滥。夫在平安无事之时。文武试取。固不宜太过。在今危急存亡之秋。岂可拘于常规。而不为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00H 页
 缓急可恃之举乎。或者又以多失军士为虑。此亦不然。其为军士也皆不可恃。及为出身则皆为可恃之军。是变无用之军。为有用之军也。且乡曲品官庶孽之辈。隐漏闲游者。多矣。闻有广取之举。则皆将出而应试。军簿之外。所得必多矣。所谓选将才者。窃见人才之乏。未有甚于此时。而将才尤为甚。臣犹记壬辰年。八道防御使,助防将一时差出。而皆有名称武将也。今则武将有人望者绝少。此极可寒心者也。虽有精兵。苟将非其人。固难于战。今既无兵又无将。其何以战乎。此极可虑者也。臣窃料天之生人。智愚才鄙有万不同。智者才者。固或不能多有。必不皆愚皆鄙。岂独于今日。全无可用之才乎。其必沈没于微末闲散之中。不为人所知者。多矣。求可用之人。必须得于此中。其搜得之道。则窃料凡人智愚才鄙。必辈流之人曾与之相接。而相熟者知之。今宜令武臣自堂上以下至训鍊奉事,禁军,诸军官以上凡在京者。各论荐人才。勿论京乡远近。或一人或数人。多小随意。其有计虑者。其有勇力者。有信义者。各称其所长。其所举多者及称道之盛者。录为一册。该曹招聚之。或察其容貌。或试其武艺。则其可用者。庶可得之矣。所谓
缓急可恃之举乎。或者又以多失军士为虑。此亦不然。其为军士也皆不可恃。及为出身则皆为可恃之军。是变无用之军。为有用之军也。且乡曲品官庶孽之辈。隐漏闲游者。多矣。闻有广取之举。则皆将出而应试。军簿之外。所得必多矣。所谓选将才者。窃见人才之乏。未有甚于此时。而将才尤为甚。臣犹记壬辰年。八道防御使,助防将一时差出。而皆有名称武将也。今则武将有人望者绝少。此极可寒心者也。虽有精兵。苟将非其人。固难于战。今既无兵又无将。其何以战乎。此极可虑者也。臣窃料天之生人。智愚才鄙有万不同。智者才者。固或不能多有。必不皆愚皆鄙。岂独于今日。全无可用之才乎。其必沈没于微末闲散之中。不为人所知者。多矣。求可用之人。必须得于此中。其搜得之道。则窃料凡人智愚才鄙。必辈流之人曾与之相接。而相熟者知之。今宜令武臣自堂上以下至训鍊奉事,禁军,诸军官以上凡在京者。各论荐人才。勿论京乡远近。或一人或数人。多小随意。其有计虑者。其有勇力者。有信义者。各称其所长。其所举多者及称道之盛者。录为一册。该曹招聚之。或察其容貌。或试其武艺。则其可用者。庶可得之矣。所谓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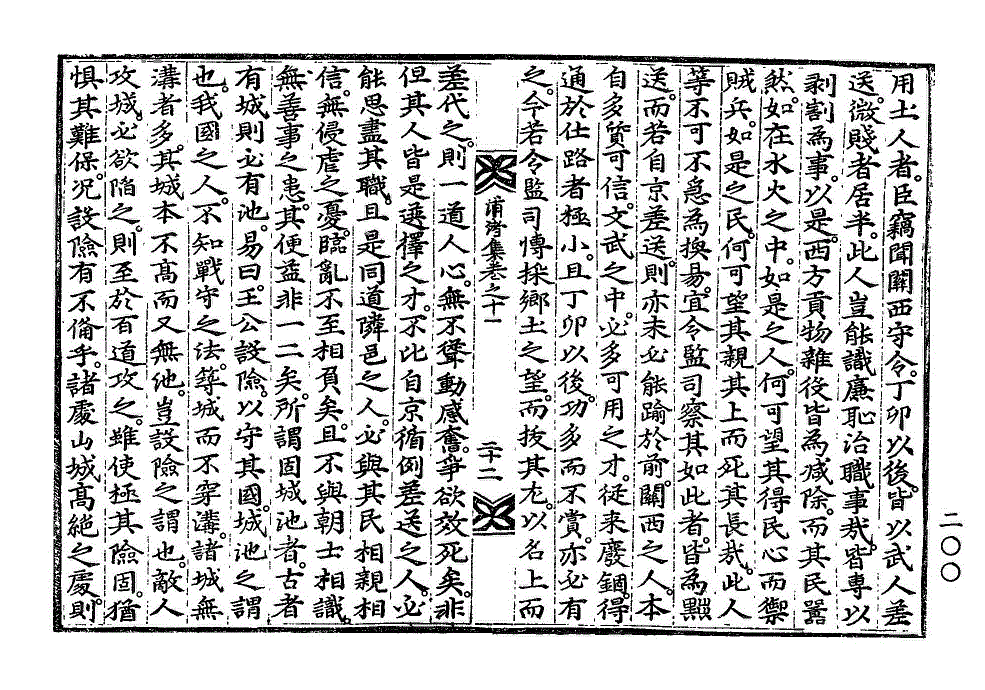 用土人者。臣窃闻关西守令。丁卯以后。皆以武人差送。微贱者居半。此人岂能识廉耻治职事哉。皆专以剥割为事。以是。西方贡物杂役皆为减除。而其民嚣然。如在水火之中。如是之人。何可望其得民心而御贼兵。如是之民。何可望其亲其上而死其长哉。此人等不可不急为换易。宜令监司察其如此者。皆为黜送。而若自京差送。则亦未必能踰于前。关西之人。本自多质可信。文武之中。必多可用之才。从来废锢。得通于仕路者极小。且丁卯以后。功多而不赏。亦必有之。今若令监司博采乡土之望。而拔其尤。以名上而差代之。则一道人心。无不耸动感奋。争欲效死矣。非但其人皆是选择之才。不比自京循例差送之人。必能思尽其职。且是同道邻邑之人。必与其民相亲相信。无侵虐之忧。临乱不至相负矣。且不与朝士相识。无善事之患。其便益非一二矣。所谓固城池者。古者有城则必有池。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城池之谓也。我国之人。不知战守之法。筑城而不穿沟。诸城无沟者多。其城本不高而又无池。岂设险之谓也。敌人攻城。必欲陷之。则至于百道攻之。虽使极其险固。犹惧其难保。况设险有不备乎。诸处山城高绝之处。则
用土人者。臣窃闻关西守令。丁卯以后。皆以武人差送。微贱者居半。此人岂能识廉耻治职事哉。皆专以剥割为事。以是。西方贡物杂役皆为减除。而其民嚣然。如在水火之中。如是之人。何可望其得民心而御贼兵。如是之民。何可望其亲其上而死其长哉。此人等不可不急为换易。宜令监司察其如此者。皆为黜送。而若自京差送。则亦未必能踰于前。关西之人。本自多质可信。文武之中。必多可用之才。从来废锢。得通于仕路者极小。且丁卯以后。功多而不赏。亦必有之。今若令监司博采乡土之望。而拔其尤。以名上而差代之。则一道人心。无不耸动感奋。争欲效死矣。非但其人皆是选择之才。不比自京循例差送之人。必能思尽其职。且是同道邻邑之人。必与其民相亲相信。无侵虐之忧。临乱不至相负矣。且不与朝士相识。无善事之患。其便益非一二矣。所谓固城池者。古者有城则必有池。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城池之谓也。我国之人。不知战守之法。筑城而不穿沟。诸城无沟者多。其城本不高而又无池。岂设险之谓也。敌人攻城。必欲陷之。则至于百道攻之。虽使极其险固。犹惧其难保。况设险有不备乎。诸处山城高绝之处。则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01H 页
 虽无沟可也。平地之城。急宜穿沟。沟外又设木栅。使贼兵不得猝至城下。稍为可恃也。且守城之具。莫如火炮。苟城池极固。火器备具。敌至。定其心志。不自恇怯。随方应之。则岂有不可守之理哉。所谓便弓制者。臣窃闻习知战陈者。多言我国角弓。实不及虏之木弓。盖我国角弓。名于天下。如使力士操劲弓以射。则其穿甲及远。非虏之所及也。然张弦日久则强反为弱。雾露沾湿则筋胶解弛。此角弓之所短也。且武士之所持角弓不多。而各官军器所藏。皆装饰外面。苟充其数。军卒所自备者。率多陈久破缺。其实皆不可用也。虏之木弓则久张而不弱。雨湿而不伤。其及远虽不如角弓。矢之所及则其发如破。且角弓能及远。故远而射之。失多虚发。木弓不能及远。故度可中而发。发则多中。故我国之弓。虽曰名于天下。其实用反不及于虏如此。夫战陈之用。器械甚要。而我国之弓。名实不同如此。此不可不变通者也。臣窃闻我国山尺等。皆以木弓射兽。而壬辰年诸处义兵。亦多以木弓杀贼。臣儿时亦尝亲见之。其制用木全条。剡其两端。其长几倍角弓。以麻或纻为弦。若加筋与漆则尤坚强云。此备之甚易。而久张耐湿。而能杀敌。则与虏
虽无沟可也。平地之城。急宜穿沟。沟外又设木栅。使贼兵不得猝至城下。稍为可恃也。且守城之具。莫如火炮。苟城池极固。火器备具。敌至。定其心志。不自恇怯。随方应之。则岂有不可守之理哉。所谓便弓制者。臣窃闻习知战陈者。多言我国角弓。实不及虏之木弓。盖我国角弓。名于天下。如使力士操劲弓以射。则其穿甲及远。非虏之所及也。然张弦日久则强反为弱。雾露沾湿则筋胶解弛。此角弓之所短也。且武士之所持角弓不多。而各官军器所藏。皆装饰外面。苟充其数。军卒所自备者。率多陈久破缺。其实皆不可用也。虏之木弓则久张而不弱。雨湿而不伤。其及远虽不如角弓。矢之所及则其发如破。且角弓能及远。故远而射之。失多虚发。木弓不能及远。故度可中而发。发则多中。故我国之弓。虽曰名于天下。其实用反不及于虏如此。夫战陈之用。器械甚要。而我国之弓。名实不同如此。此不可不变通者也。臣窃闻我国山尺等。皆以木弓射兽。而壬辰年诸处义兵。亦多以木弓杀贼。臣儿时亦尝亲见之。其制用木全条。剡其两端。其长几倍角弓。以麻或纻为弦。若加筋与漆则尤坚强云。此备之甚易。而久张耐湿。而能杀敌。则与虏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01L 页
 弓无异。臣窃以为宜多备此弓。武士所持劲弓。固不可废。若军人之弓不可用者。令以此弓代之。使军中角木相杂。则其角弓皆为劲弓。自可尽我国之技。而木弓与虏技相当。实为便益也。所谓导民人者。贼若深入。则军兵皆收入于城中。民人男女各自奔窜。贼必布散搜索。无处不到。而无可御之计。任其杀掳。此实莫大之患也。今宜以木弓之制。教之民间。凡男子胜兵者。皆使持之。盖此弓备之甚易。其技又为之甚易。人人所可备者也。所可能也。而其利则可以杀敌而卫身也。贼来。使村民各聚而成群。海边之地则入于岛。有山城旧址处则略为修筑而入守。有山则入于山。皆持此弓而御之。贼之掳掠者。其数不多。苟处处十百为群而射之。则自可免于俘虏。而虽或不免于死。亦可杀贼而死。不为独死矣。丁卯之变。贼或数名。驱男女百馀人。而靡然被驱。不敢违拒者。以手中无兵器也。使其时人人有此弓。则岂不能杀贼。而拱手就驱乎。此实制虏而卫吾民之一策也。宜令西路各邑。以此晓喻其民。使村村家家皆知此意。皆备此弓以待也。西路竹箭难得。以木为之如虏矢亦可也。若国中改纪之方。则臣窃念今之大可忧者。唯在于
弓无异。臣窃以为宜多备此弓。武士所持劲弓。固不可废。若军人之弓不可用者。令以此弓代之。使军中角木相杂。则其角弓皆为劲弓。自可尽我国之技。而木弓与虏技相当。实为便益也。所谓导民人者。贼若深入。则军兵皆收入于城中。民人男女各自奔窜。贼必布散搜索。无处不到。而无可御之计。任其杀掳。此实莫大之患也。今宜以木弓之制。教之民间。凡男子胜兵者。皆使持之。盖此弓备之甚易。其技又为之甚易。人人所可备者也。所可能也。而其利则可以杀敌而卫身也。贼来。使村民各聚而成群。海边之地则入于岛。有山城旧址处则略为修筑而入守。有山则入于山。皆持此弓而御之。贼之掳掠者。其数不多。苟处处十百为群而射之。则自可免于俘虏。而虽或不免于死。亦可杀贼而死。不为独死矣。丁卯之变。贼或数名。驱男女百馀人。而靡然被驱。不敢违拒者。以手中无兵器也。使其时人人有此弓。则岂不能杀贼。而拱手就驱乎。此实制虏而卫吾民之一策也。宜令西路各邑。以此晓喻其民。使村村家家皆知此意。皆备此弓以待也。西路竹箭难得。以木为之如虏矢亦可也。若国中改纪之方。则臣窃念今之大可忧者。唯在于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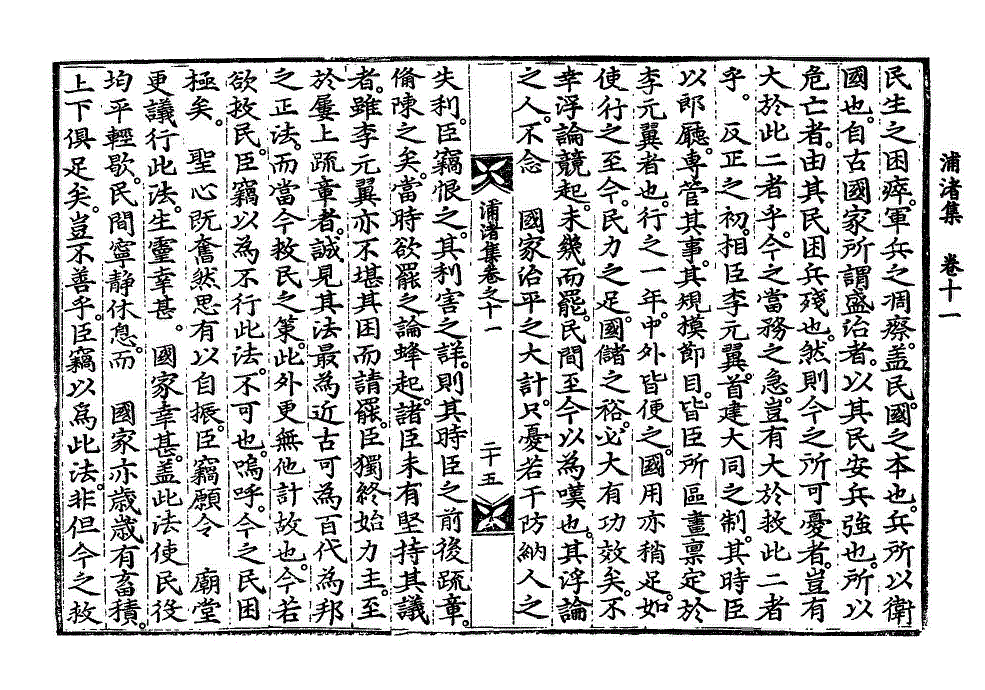 民生之困瘁。军兵之凋瘵。盖民。国之本也。兵所以卫国也。自古国家所谓盛治者。以其民安兵强也。所以危亡者。由其民困兵残也。然则今之所可忧者。岂有大于此二者乎。今之当务之急。岂有大于救此二者乎。 反正之初。相臣李元翼。首建大同之制。其时臣以郎厅。专管其事。其规模节目。皆臣所区画禀定于李元翼者也。行之一年。中外皆便之。国用亦稍足。如使行之至今。民力之足。国储之裕。必大有功效矣。不幸浮论竞起。未几而罢。民间至今以为叹也。其浮论之人。不念 国家治平之大计。只忧若干防纳人之失利。臣窃恨之。其利害之详。则其时臣之前后疏章。备陈之矣。当时欲罢之论蜂起。诸臣未有坚持其议者。虽李元翼亦不堪其困而请罢。臣独终始力主。至于屡上疏章者。诚见其法最为近古可为百代为邦之正法。而当今救民之策。此外更无他计故也。今若欲救民。臣窃以为不行此法。不可也。呜呼。今之民困极矣。 圣心既奋然思有以自振。臣窃愿令 庙堂更议行此法。生灵幸甚。 国家幸甚。盖此法使民役均平轻歇。民间宁静休息。而 国家亦岁岁有畜积。上下俱足矣。岂不善乎。臣窃以为此法。非但今之救
民生之困瘁。军兵之凋瘵。盖民。国之本也。兵所以卫国也。自古国家所谓盛治者。以其民安兵强也。所以危亡者。由其民困兵残也。然则今之所可忧者。岂有大于此二者乎。今之当务之急。岂有大于救此二者乎。 反正之初。相臣李元翼。首建大同之制。其时臣以郎厅。专管其事。其规模节目。皆臣所区画禀定于李元翼者也。行之一年。中外皆便之。国用亦稍足。如使行之至今。民力之足。国储之裕。必大有功效矣。不幸浮论竞起。未几而罢。民间至今以为叹也。其浮论之人。不念 国家治平之大计。只忧若干防纳人之失利。臣窃恨之。其利害之详。则其时臣之前后疏章。备陈之矣。当时欲罢之论蜂起。诸臣未有坚持其议者。虽李元翼亦不堪其困而请罢。臣独终始力主。至于屡上疏章者。诚见其法最为近古可为百代为邦之正法。而当今救民之策。此外更无他计故也。今若欲救民。臣窃以为不行此法。不可也。呜呼。今之民困极矣。 圣心既奋然思有以自振。臣窃愿令 庙堂更议行此法。生灵幸甚。 国家幸甚。盖此法使民役均平轻歇。民间宁静休息。而 国家亦岁岁有畜积。上下俱足矣。岂不善乎。臣窃以为此法。非但今之救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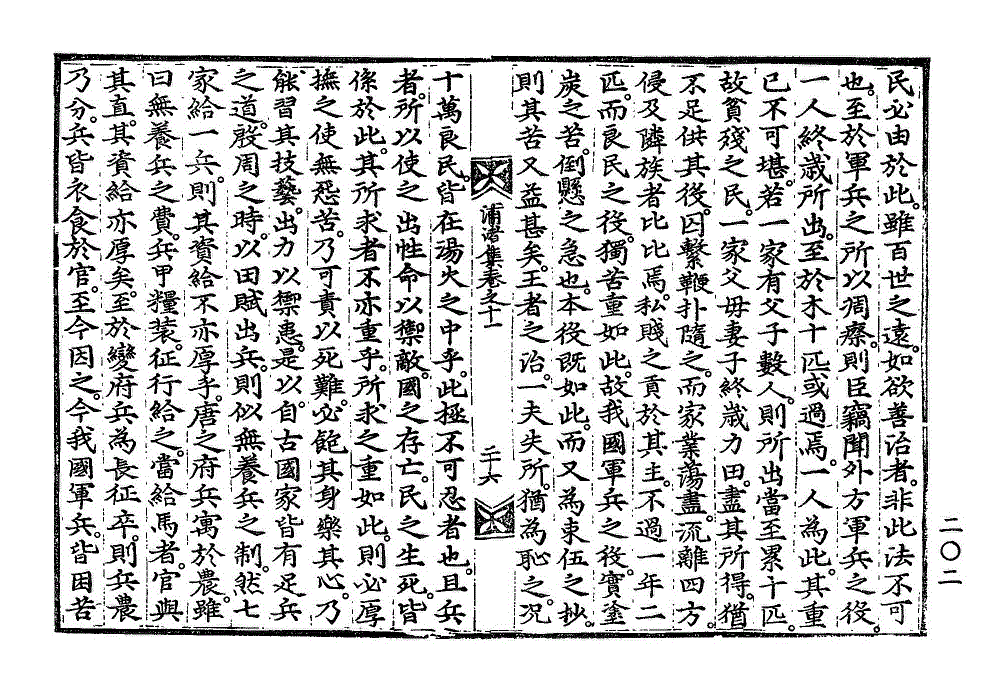 民必由于此。虽百世之远。如欲善治者。非此法不可也。至于军兵之所以凋瘵。则臣窃闻外方军兵之役。一人终岁所出。至于木十匹或过焉。一人为此。其重已不可堪。若一家有父子数人。则所出当至累十匹。故贫残之民。一家父母妻子终岁力田。尽其所得。犹不足供其役。囚系鞭扑随之。而家业荡尽。流离四方。侵及邻族者比比焉。私贱之贡于其主。不过一年二匹。而良民之役。独苦重如此。故我国军兵之役。实涂炭之苦。倒悬之急也。本役既如此。而又为束伍之抄。则其苦又益甚矣。王者之治。一夫失所。犹为耻之。况十万良民。皆在汤火之中乎。此极不可忍者也。且兵者。所以使之出性命以御敌。国之存亡。民之生死。皆系于此。其所求者不亦重乎。所求之重如此。则必厚抚之使无怨苦。乃可责以死难。必饱其身乐其心。乃能习其技艺。出力以御患。是以。自古国家皆有足兵之道。殷周之时。以田赋出兵。则似无养兵之制。然七家给一兵。则其资给不亦厚乎。唐之府兵寓于农。虽曰无养兵之费。兵甲粮装。征行给之。当给马者。官与其直。其资给亦厚矣。至于变府兵为长征卒。则兵农乃分。兵皆衣食于官。至今因之。今我国军兵。皆困苦
民必由于此。虽百世之远。如欲善治者。非此法不可也。至于军兵之所以凋瘵。则臣窃闻外方军兵之役。一人终岁所出。至于木十匹或过焉。一人为此。其重已不可堪。若一家有父子数人。则所出当至累十匹。故贫残之民。一家父母妻子终岁力田。尽其所得。犹不足供其役。囚系鞭扑随之。而家业荡尽。流离四方。侵及邻族者比比焉。私贱之贡于其主。不过一年二匹。而良民之役。独苦重如此。故我国军兵之役。实涂炭之苦。倒悬之急也。本役既如此。而又为束伍之抄。则其苦又益甚矣。王者之治。一夫失所。犹为耻之。况十万良民。皆在汤火之中乎。此极不可忍者也。且兵者。所以使之出性命以御敌。国之存亡。民之生死。皆系于此。其所求者不亦重乎。所求之重如此。则必厚抚之使无怨苦。乃可责以死难。必饱其身乐其心。乃能习其技艺。出力以御患。是以。自古国家皆有足兵之道。殷周之时。以田赋出兵。则似无养兵之制。然七家给一兵。则其资给不亦厚乎。唐之府兵寓于农。虽曰无养兵之费。兵甲粮装。征行给之。当给马者。官与其直。其资给亦厚矣。至于变府兵为长征卒。则兵农乃分。兵皆衣食于官。至今因之。今我国军兵。皆困苦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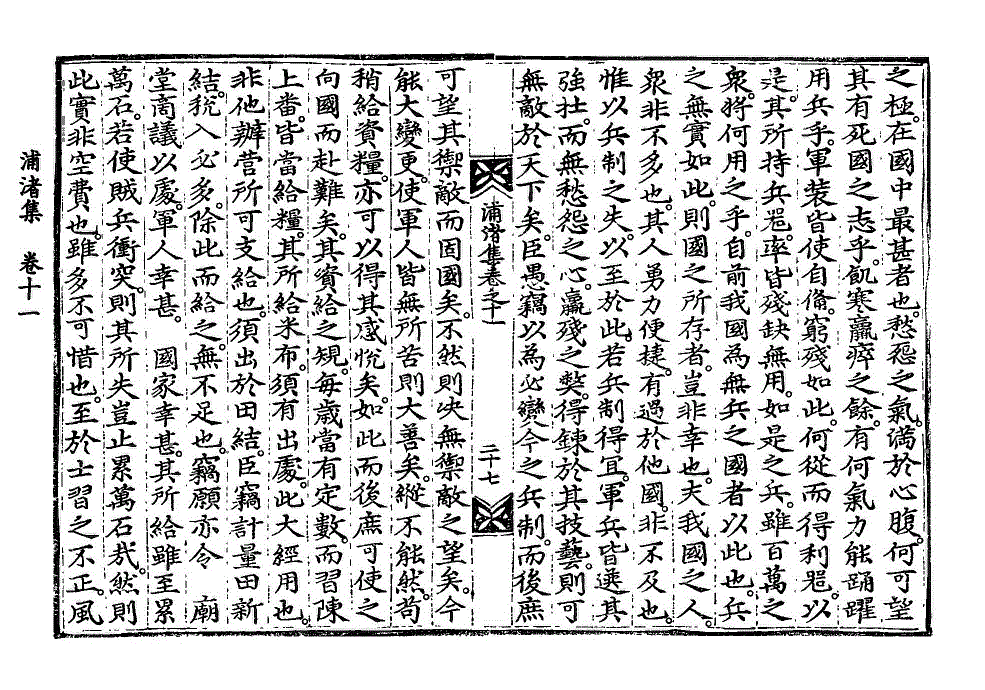 之极。在国中最甚者也。愁怨之气。满于心腹。何可望其有死国之志乎。饥寒羸瘁之馀。有何气力能踊跃用兵乎。军装皆使自备。穷残如此。何从而得利器。以是。其所持兵器。率皆残缺无用。如是之兵。虽百万之众。将何用之乎。自前我国为无兵之国者以此也。兵之无实知此。则国之所存者。岂非幸也。夫我国之人。众非不多也。其人勇力便捷。有过于他国。非不及也。惟以兵制之失。以至于此。若兵制得宜。军兵皆选其强壮。而无愁怨之心。羸残之弊。得鍊于其技艺。则可无敌于天下矣。臣愚窃以为必变今之兵制。而后庶可望其御敌而固国矣。不然则决无御敌之望矣。今能大变更。使军人皆无所苦则大善矣。纵不能然。苟稍给资粮。亦可以得其感悦矣。如此而后庶可使之向国而赴难矣。其资给之规。每岁当有定数。而习陈上番。皆当给粮。其所给米布。须有出处。此大经用也。非他办营所可支给也。须出于田结。臣窃计量田新结。税入必多。除此而给之。无不足也。窃愿亦令 庙堂商议以处。军人幸甚。 国家幸甚。其所给虽至累万石。若使贼兵冲突。则其所失岂止累万石哉。然则此实非空费也。虽多不可惜也。至于士习之不正。风
之极。在国中最甚者也。愁怨之气。满于心腹。何可望其有死国之志乎。饥寒羸瘁之馀。有何气力能踊跃用兵乎。军装皆使自备。穷残如此。何从而得利器。以是。其所持兵器。率皆残缺无用。如是之兵。虽百万之众。将何用之乎。自前我国为无兵之国者以此也。兵之无实知此。则国之所存者。岂非幸也。夫我国之人。众非不多也。其人勇力便捷。有过于他国。非不及也。惟以兵制之失。以至于此。若兵制得宜。军兵皆选其强壮。而无愁怨之心。羸残之弊。得鍊于其技艺。则可无敌于天下矣。臣愚窃以为必变今之兵制。而后庶可望其御敌而固国矣。不然则决无御敌之望矣。今能大变更。使军人皆无所苦则大善矣。纵不能然。苟稍给资粮。亦可以得其感悦矣。如此而后庶可使之向国而赴难矣。其资给之规。每岁当有定数。而习陈上番。皆当给粮。其所给米布。须有出处。此大经用也。非他办营所可支给也。须出于田结。臣窃计量田新结。税入必多。除此而给之。无不足也。窃愿亦令 庙堂商议以处。军人幸甚。 国家幸甚。其所给虽至累万石。若使贼兵冲突。则其所失岂止累万石哉。然则此实非空费也。虽多不可惜也。至于士习之不正。风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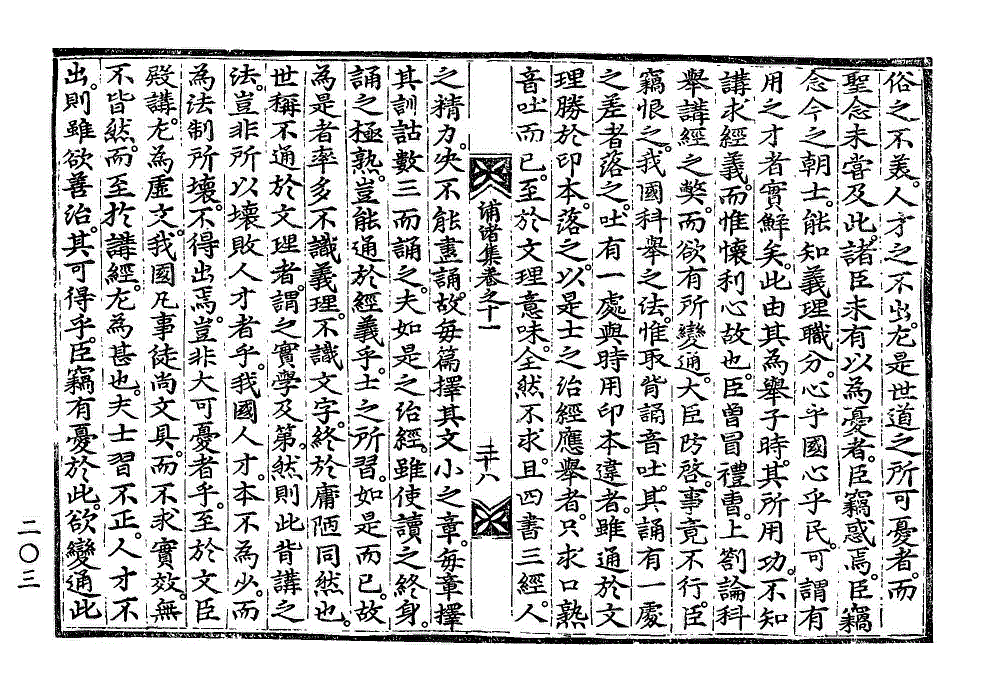 俗之不美。人才之不出。尤是世道之所可忧者。而 圣念未尝及此。诸臣未有以为忧者。臣窃惑焉。臣窃念今之朝士。能知义理职分。心乎国心乎民。可谓有用之才者实鲜矣。此由其为举子时。其所用功。不知讲求经义。而惟怀利心故也。臣曾冒礼曹。上劄论科举讲经之弊。而欲有所变通。大臣防启。事竟不行。臣窃恨之。我国科举之法。惟取背诵音吐。其诵有一处之差者落之。吐有一处与时用印本违者。虽通于文理胜于印本。落之。以是士之治经应举者。只求口熟音吐而已。至于文理意味。全然不求。且四书三经。人之精力。决不能尽诵。故每篇择其文小之章。每章择其训诂数三而诵之。夫如是之治经。虽使读之终身。诵之极熟。岂能通于经义乎。士之所习。如是而已。故为是者率多不识义理。不识文字。终于庸陋同然也。世称不通于文理者。谓之实学及第。然则此背讲之法。岂非所以坏败人才者乎。我国人才。本不为少。而为法制所坏。不得出焉。岂非大可忧者乎。至于文臣殿讲。尤为虚文。我国凡事徒尚文具。而不求实效。无不皆然。而至于讲经。尤为甚也。夫士习不正。人才不出。则虽欲善治。其可得乎。臣窃有忧于此。欲变通此
俗之不美。人才之不出。尤是世道之所可忧者。而 圣念未尝及此。诸臣未有以为忧者。臣窃惑焉。臣窃念今之朝士。能知义理职分。心乎国心乎民。可谓有用之才者实鲜矣。此由其为举子时。其所用功。不知讲求经义。而惟怀利心故也。臣曾冒礼曹。上劄论科举讲经之弊。而欲有所变通。大臣防启。事竟不行。臣窃恨之。我国科举之法。惟取背诵音吐。其诵有一处之差者落之。吐有一处与时用印本违者。虽通于文理胜于印本。落之。以是士之治经应举者。只求口熟音吐而已。至于文理意味。全然不求。且四书三经。人之精力。决不能尽诵。故每篇择其文小之章。每章择其训诂数三而诵之。夫如是之治经。虽使读之终身。诵之极熟。岂能通于经义乎。士之所习。如是而已。故为是者率多不识义理。不识文字。终于庸陋同然也。世称不通于文理者。谓之实学及第。然则此背讲之法。岂非所以坏败人才者乎。我国人才。本不为少。而为法制所坏。不得出焉。岂非大可忧者乎。至于文臣殿讲。尤为虚文。我国凡事徒尚文具。而不求实效。无不皆然。而至于讲经。尤为甚也。夫士习不正。人才不出。则虽欲善治。其可得乎。臣窃有忧于此。欲变通此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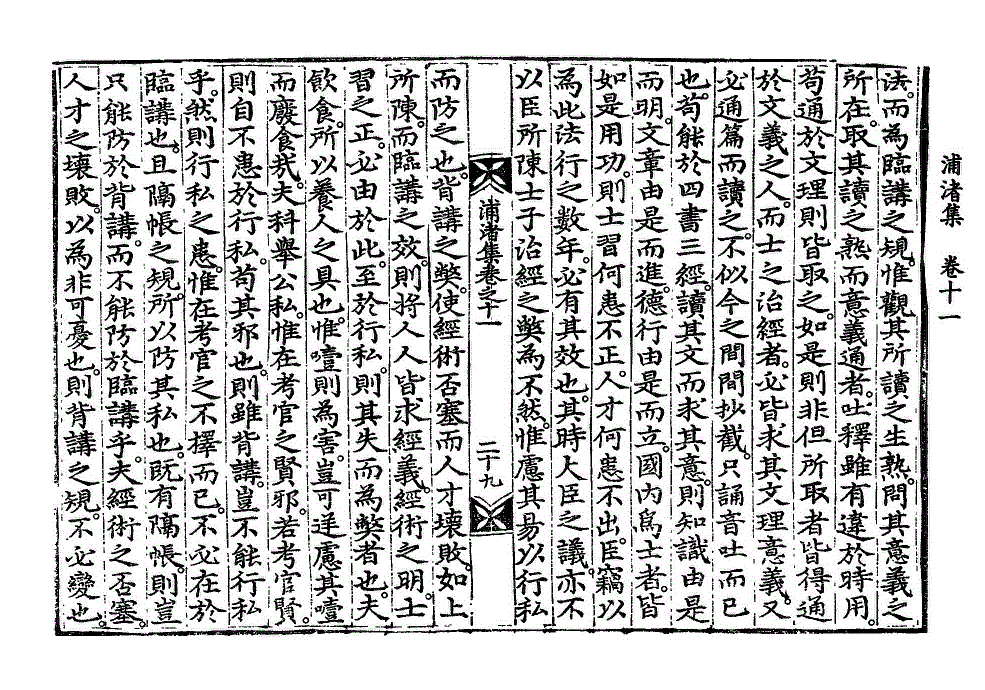 法。而为临讲之规。惟观其所读之生熟。问其意义之所在。取其读之熟而意义通者。吐释虽有违于时用。苟通于文理则皆取之。如是则非但所取者皆得通于文义之人。而士之治经者。必皆求其文理意义。又必通篇而读之。不似今之间间抄截。只诵音吐而已也。苟能于四书三经。读其文而求其意。则知识由是而明。文章由是而进。德行由是而立。国内为士者。皆如是用功。则士习何患不正。人才何患不出。臣窃以为此法行之数年。必有其效也。其时大臣之议。亦不以臣所陈士子治经之弊为不然。惟虑其易以行私而防之也。背讲之弊。使经术否塞而人才坏败。如上所陈。而临讲之效。则将人人皆求经义。经术之明。士习之正。必由于此。至于行私。则其失而为弊者也。夫饮食。所以养人之具也。惟噎则为害。岂可逆虑其噎而废食哉。夫科举公私。惟在考官之贤邪。若考官贤。则自不患于行私。苟其邪也。则虽背讲。岂不能行私乎。然则行私之患。惟在考官之不择而已。不必在于临讲也。且隔帐之规。所以防其私也。既有隔帐。则岂只能防于背讲。而不能防于临讲乎。夫经术之否塞。人才之坏败。以为非可忧也。则背讲之规。不必变也。
法。而为临讲之规。惟观其所读之生熟。问其意义之所在。取其读之熟而意义通者。吐释虽有违于时用。苟通于文理则皆取之。如是则非但所取者皆得通于文义之人。而士之治经者。必皆求其文理意义。又必通篇而读之。不似今之间间抄截。只诵音吐而已也。苟能于四书三经。读其文而求其意。则知识由是而明。文章由是而进。德行由是而立。国内为士者。皆如是用功。则士习何患不正。人才何患不出。臣窃以为此法行之数年。必有其效也。其时大臣之议。亦不以臣所陈士子治经之弊为不然。惟虑其易以行私而防之也。背讲之弊。使经术否塞而人才坏败。如上所陈。而临讲之效。则将人人皆求经义。经术之明。士习之正。必由于此。至于行私。则其失而为弊者也。夫饮食。所以养人之具也。惟噎则为害。岂可逆虑其噎而废食哉。夫科举公私。惟在考官之贤邪。若考官贤。则自不患于行私。苟其邪也。则虽背讲。岂不能行私乎。然则行私之患。惟在考官之不择而已。不必在于临讲也。且隔帐之规。所以防其私也。既有隔帐。则岂只能防于背讲。而不能防于临讲乎。夫经术之否塞。人才之坏败。以为非可忧也。则背讲之规。不必变也。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04L 页
 如以为可忧也。则不变此法。终无可救之理也。此臣之复此恳恳。不自知止者也。如财赋军政。其变更也。措画施设。未免烦劳。此法之改。则只是讲定命下而已。小无烦劳之事。何难而不为乎。行之数年。若无其效。则还复旧制。亦非有害也。窃愿 睿察断而行之。则多士幸甚。世道幸甚。此三者皆今日为国之大制度。如此则民安兵强而士习正矣。国之治岂有加于此哉。此皆臣区区一得。常所藏之心中者也。今因 圣志之奋发。敢罄竭底蕴。仰备 采择。然此则治之法也。至于治之道。则所谓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是也。 圣明虽无失德。间或有不能由法度者。则是所谓衮职有阙。君心之非者也。苟不能察而改之。则将至于罔念作狂。而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窃愿勿以小过而忽之。省察克治之功。不可须臾息也。且今此 圣心之奋发。实天理之正也。诚能继此兢业而守之。讲学而明之。不使此心小有间断。则其发于言语政事之间者。皆将一出于正。而虽或有纤毫过差萌于其间。亦皆知而去之。不至为 圣德之累矣。至于 朝廷之上。所用多是善人长者。则 殿下之用人。可谓得矣。然其间或未免有杂进者。且不正不公
如以为可忧也。则不变此法。终无可救之理也。此臣之复此恳恳。不自知止者也。如财赋军政。其变更也。措画施设。未免烦劳。此法之改。则只是讲定命下而已。小无烦劳之事。何难而不为乎。行之数年。若无其效。则还复旧制。亦非有害也。窃愿 睿察断而行之。则多士幸甚。世道幸甚。此三者皆今日为国之大制度。如此则民安兵强而士习正矣。国之治岂有加于此哉。此皆臣区区一得。常所藏之心中者也。今因 圣志之奋发。敢罄竭底蕴。仰备 采择。然此则治之法也。至于治之道。则所谓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是也。 圣明虽无失德。间或有不能由法度者。则是所谓衮职有阙。君心之非者也。苟不能察而改之。则将至于罔念作狂。而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窃愿勿以小过而忽之。省察克治之功。不可须臾息也。且今此 圣心之奋发。实天理之正也。诚能继此兢业而守之。讲学而明之。不使此心小有间断。则其发于言语政事之间者。皆将一出于正。而虽或有纤毫过差萌于其间。亦皆知而去之。不至为 圣德之累矣。至于 朝廷之上。所用多是善人长者。则 殿下之用人。可谓得矣。然其间或未免有杂进者。且不正不公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05H 页
 之事。亦多有人言之藉藉。夫杂进之弊。善恶不分。私欲之行。天理灭息。其为清朝之害。亦岂可胜言也哉。然凡人贤否邪正。皆形于言行。自不可掩。以 圣智之明。苟察于此则岂患不知。如知其为贤为正。则任之而勿贰。知其为否为邪。则去之而勿疑。则好恶既明。善恶自分矣。若知其贤而不能用。知其不贤而不能去。则是无益于知。而朝廷何由而正。郭公之亡。正坐于此。然则其所患不在于不知。惟在于知而不能用不能去耳。然人之知识。或有所不及。虽圣人。未能必其无所不及。然则 圣躬有阙。容或有未及自知者。朝臣贤否。亦未必皆知而无失。至于外间之事。固无由得闻。自古置谏诤之官。使之无所不言。以此也。如取公明正直自前能敢谏直言之士。常列于耳目之职。则自 圣躬之阙失。至于朝臣贤否善恶。可得以尽闻矣。凡此所陈。皆区区愚忠所竭意。而思仰冀有所裨补者也。伏惟 圣明不以臣之愚。而留神澄省焉。取 进止。
之事。亦多有人言之藉藉。夫杂进之弊。善恶不分。私欲之行。天理灭息。其为清朝之害。亦岂可胜言也哉。然凡人贤否邪正。皆形于言行。自不可掩。以 圣智之明。苟察于此则岂患不知。如知其为贤为正。则任之而勿贰。知其为否为邪。则去之而勿疑。则好恶既明。善恶自分矣。若知其贤而不能用。知其不贤而不能去。则是无益于知。而朝廷何由而正。郭公之亡。正坐于此。然则其所患不在于不知。惟在于知而不能用不能去耳。然人之知识。或有所不及。虽圣人。未能必其无所不及。然则 圣躬有阙。容或有未及自知者。朝臣贤否。亦未必皆知而无失。至于外间之事。固无由得闻。自古置谏诤之官。使之无所不言。以此也。如取公明正直自前能敢谏直言之士。常列于耳目之职。则自 圣躬之阙失。至于朝臣贤否善恶。可得以尽闻矣。凡此所陈。皆区区愚忠所竭意。而思仰冀有所裨补者也。伏惟 圣明不以臣之愚。而留神澄省焉。取 进止。论待倭事劄
伏以臣昨见东莱府使状启。李亨男与藤倭问答之辞。藤倭所请。必欲改救灾恤邻之道。非常难再之恩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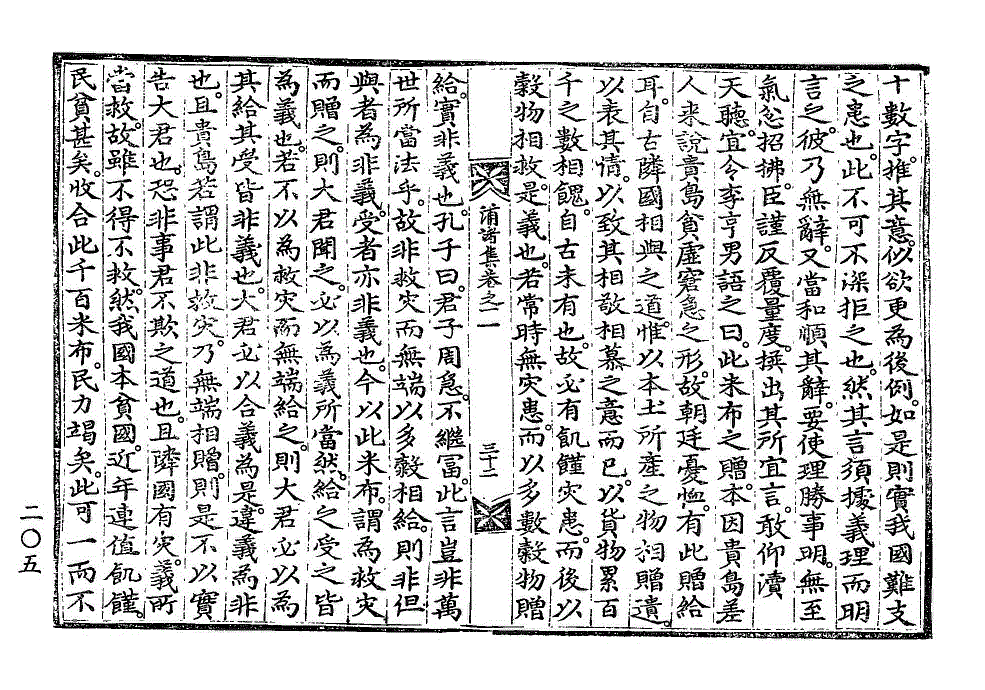 十数字。推其意。似欲更为后例。如是则实我国难支之患也。此不可不深拒之也。然其言须据义理而明言之。彼乃无辞。又当和顺其辞。要使理胜事明。无至气忿招拂。臣谨反覆量度。撰出其所宜言。敢仰渎 天听。宜令李亨男语之曰。此米布之赠。本因贵岛差人来说贵岛贫虚窘急之形。故朝廷忧恤。有此赠给耳。自古邻国相与之道。惟以本土所产之物相赠遗。以表其情。以致其相敬相慕之意而已。以货物累百千之数相馈。自古未有也。故必有饥馑灾患。而后以谷物相救。是义也。若常时无灾患。而以多数谷物赠给。实非义也。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继富。此言岂非万世所当法乎。故非救灾而无端以多谷相给。则非但与者为非义。受者亦非义也。今以此米布。谓为救灾而赠之。则大君闻之。必以为义所当然。给之受之皆为义也。若不以为救灾而无端给之。则大君必以为其给其受皆非义也。大君必以合义为是。违义为非也。且贵岛若谓此非救灾。乃无端相赠。则是不以实告大君也。恐非事君不欺之道也。且邻国有灾。义所当救。故虽不得不救。然我国本贫国。近年连值饥馑。民贫甚矣。收合此千百米布。民力竭矣。此可一而不
十数字。推其意。似欲更为后例。如是则实我国难支之患也。此不可不深拒之也。然其言须据义理而明言之。彼乃无辞。又当和顺其辞。要使理胜事明。无至气忿招拂。臣谨反覆量度。撰出其所宜言。敢仰渎 天听。宜令李亨男语之曰。此米布之赠。本因贵岛差人来说贵岛贫虚窘急之形。故朝廷忧恤。有此赠给耳。自古邻国相与之道。惟以本土所产之物相赠遗。以表其情。以致其相敬相慕之意而已。以货物累百千之数相馈。自古未有也。故必有饥馑灾患。而后以谷物相救。是义也。若常时无灾患。而以多数谷物赠给。实非义也。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继富。此言岂非万世所当法乎。故非救灾而无端以多谷相给。则非但与者为非义。受者亦非义也。今以此米布。谓为救灾而赠之。则大君闻之。必以为义所当然。给之受之皆为义也。若不以为救灾而无端给之。则大君必以为其给其受皆非义也。大君必以合义为是。违义为非也。且贵岛若谓此非救灾。乃无端相赠。则是不以实告大君也。恐非事君不欺之道也。且邻国有灾。义所当救。故虽不得不救。然我国本贫国。近年连值饥馑。民贫甚矣。收合此千百米布。民力竭矣。此可一而不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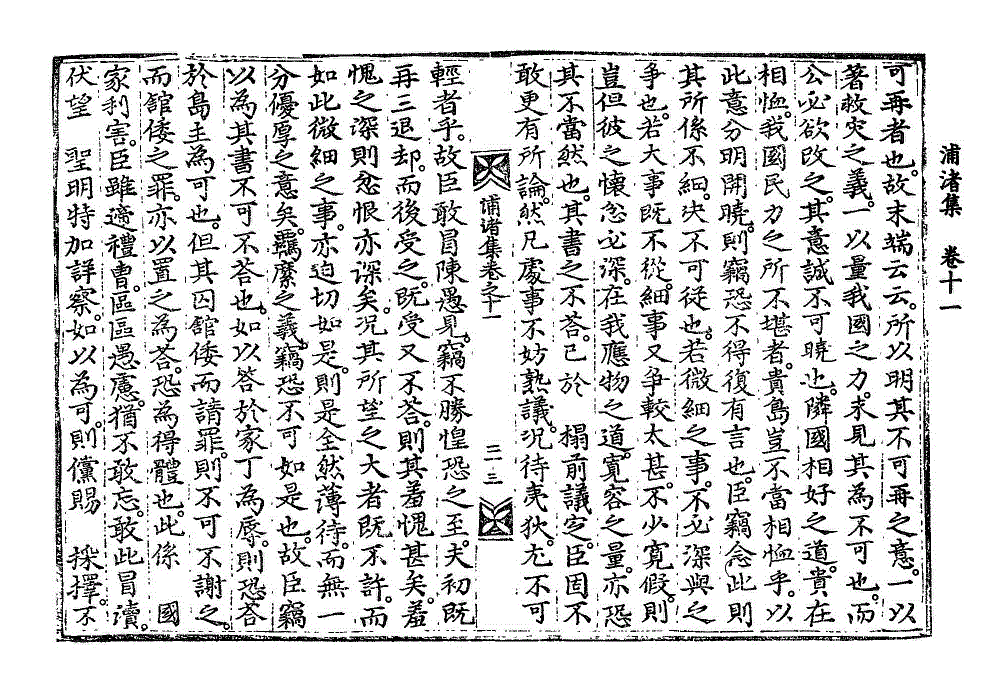 可再者也。故末端云云。所以明其不可再之意。一以著救灾之义。一以量我国之力。未见其为不可也。而公必欲改之。其意诚不可晓也。邻国相好之道。贵在相恤。我国民力之所不堪者。贵岛岂不当相恤乎。以此意分明开晓。则窃恐不得复有言也。臣窃念此则其所系不细。决不可从也。若微细之事。不必深与之争也。若大事既不从。细事又争较太甚。不少宽假。则岂但彼之怀忿必深。在我应物之道。宽容之量。亦恐其不当然也。其书之不答。已于 榻前议定。臣固不敢更有所论。然凡处事不妨熟议。况待夷狄。尤不可轻者乎。故臣敢冒陈愚见。窃不胜惶恐之至。夫初既再三退却。而后受之。既受又不答。则其羞愧甚矣。羞愧之深则忿恨亦深矣。况其所望之大者既不许。而如此微细之事。亦迫切如是。则是全然薄待。而无一分优厚之意矣。羁縻之义。窃恐不可如是也。故臣窃以为其书不可不答也。如以答于家丁为辱。则恐答于岛主为可也。但其囚馆倭而请罪。则不可不谢之。而馆倭之罪。亦以置之为答。恐为得体也。此系 国家利害。臣虽递礼曹。区区愚虑。犹不敢忘。敢此冒渎。伏望 圣明特加详察。如以为可。则傥赐 采择。不
可再者也。故末端云云。所以明其不可再之意。一以著救灾之义。一以量我国之力。未见其为不可也。而公必欲改之。其意诚不可晓也。邻国相好之道。贵在相恤。我国民力之所不堪者。贵岛岂不当相恤乎。以此意分明开晓。则窃恐不得复有言也。臣窃念此则其所系不细。决不可从也。若微细之事。不必深与之争也。若大事既不从。细事又争较太甚。不少宽假。则岂但彼之怀忿必深。在我应物之道。宽容之量。亦恐其不当然也。其书之不答。已于 榻前议定。臣固不敢更有所论。然凡处事不妨熟议。况待夷狄。尤不可轻者乎。故臣敢冒陈愚见。窃不胜惶恐之至。夫初既再三退却。而后受之。既受又不答。则其羞愧甚矣。羞愧之深则忿恨亦深矣。况其所望之大者既不许。而如此微细之事。亦迫切如是。则是全然薄待。而无一分优厚之意矣。羁縻之义。窃恐不可如是也。故臣窃以为其书不可不答也。如以答于家丁为辱。则恐答于岛主为可也。但其囚馆倭而请罪。则不可不谢之。而馆倭之罪。亦以置之为答。恐为得体也。此系 国家利害。臣虽递礼曹。区区愚虑。犹不敢忘。敢此冒渎。伏望 圣明特加详察。如以为可。则傥赐 采择。不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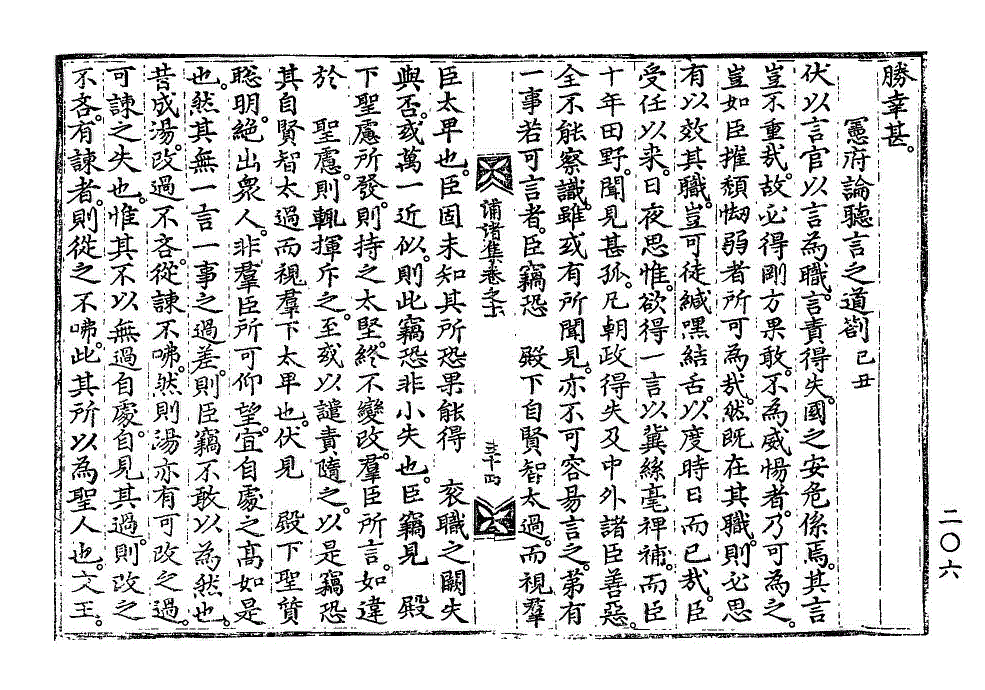 胜幸甚。
胜幸甚。宪府论听言之道劄(己丑)
伏以言官以言为职。言责得失。国之安危系焉。其言岂不重哉。故必得刚方果敢。不为威惕者。乃可为之。岂如臣摧颓怯弱者所可为哉。然既在其职。则必思有以效其职。岂可徒缄默结舌。以度时日而已哉。臣受任以来。日夜思惟。欲得一言以冀丝毫裨补。而臣十年田野。闻见甚孤。凡朝政得失及中外诸臣善恶。全不能察识。虽或有所闻见。亦不可容易言之。第有一事若可言者。臣窃恐 殿下自贤智太过。而视群臣太卑也。臣固未知其所恐果能得 衮职之阙失与否。或万一近似。则此窃恐非小失也。臣窃见 殿下圣虑所发。则持之太坚。终不变改。群臣所言。如违于 圣虑。则辄挥斥之。至或以谴责随之。以是窃恐其自贤智太过而视群下太卑也。伏见 殿下圣质聪明。绝出众人。非群臣所可仰望。宜自处之高如是也。然其无一言一事之过差。则臣窃不敢以为然也。昔成汤。改过不吝。从谏不咈。然则汤亦有可改之过。可谏之失也。惟其不以无过自处。自见其过。则改之不吝。有谏者。则从之不咈。此其所以为圣人也。文王。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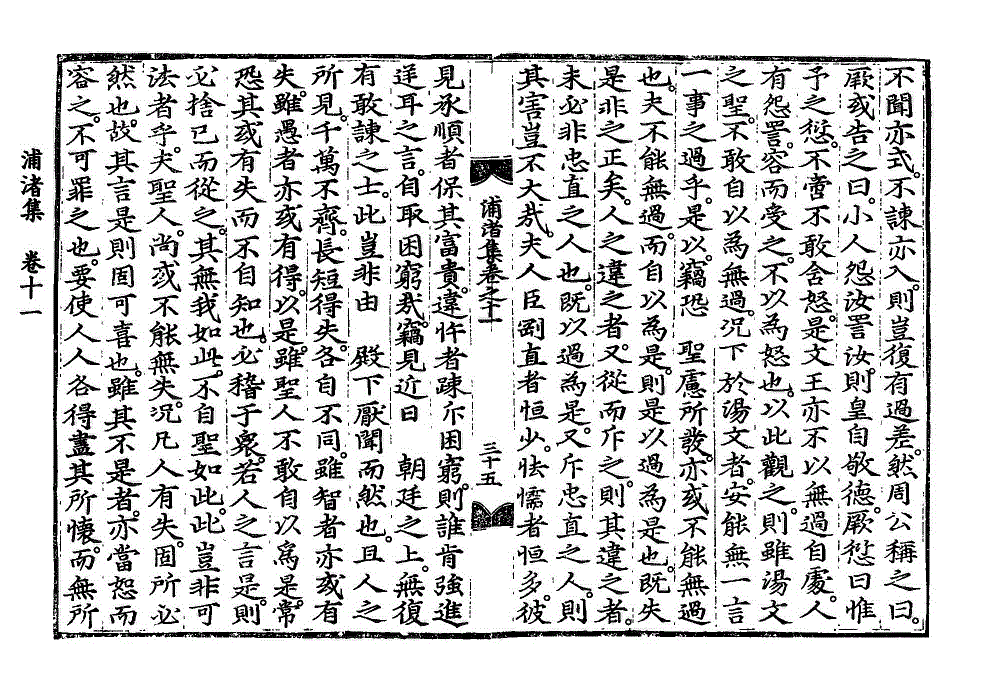 不闻亦式。不谏亦入。则岂复有过差。然周公称之曰。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惟予之愆。不啻不敢含怒。是文王亦不以无过自处。人有怨詈。容而受之。不以为怒也。以此观之。则虽汤文之圣。不敢自以为无过。况下于汤文者。安能无一言一事之过乎。是以。窃恐 圣虑所发。亦或不能无过也。夫不能无过。而自以为是。则是以过为是也。既失是非之正矣。人之违之者。又从而斥之。则其违之者。未必非忠直之人也。既以过为是。又斥忠直之人。则其害岂不大哉。夫人臣刚直者恒少。怯懦者恒多。彼见承顺者保其富贵。违忤者疏斥困穷。则谁肯强进逆耳之言。自取困穷哉。窃见近日 朝廷之上。无复有敢谏之士。此岂非由 殿下厌闻而然也。且人之所见。千万不齐。长短得失。各自不同。虽智者亦或有失。虽愚者亦或有得。以是。虽圣人不敢自以为是。常恐其或有失而不自知也。必稽于众。若人之言是。则必舍己而从之。其无我如此。不自圣如此。此岂非可法者乎。夫圣人。尚或不能无失。况凡人有失。固所必然也。故其言是则固可喜也。虽其不是者。亦当恕而容之。不可罪之也。要使人人各得尽其所怀。而无所
不闻亦式。不谏亦入。则岂复有过差。然周公称之曰。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惟予之愆。不啻不敢含怒。是文王亦不以无过自处。人有怨詈。容而受之。不以为怒也。以此观之。则虽汤文之圣。不敢自以为无过。况下于汤文者。安能无一言一事之过乎。是以。窃恐 圣虑所发。亦或不能无过也。夫不能无过。而自以为是。则是以过为是也。既失是非之正矣。人之违之者。又从而斥之。则其违之者。未必非忠直之人也。既以过为是。又斥忠直之人。则其害岂不大哉。夫人臣刚直者恒少。怯懦者恒多。彼见承顺者保其富贵。违忤者疏斥困穷。则谁肯强进逆耳之言。自取困穷哉。窃见近日 朝廷之上。无复有敢谏之士。此岂非由 殿下厌闻而然也。且人之所见。千万不齐。长短得失。各自不同。虽智者亦或有失。虽愚者亦或有得。以是。虽圣人不敢自以为是。常恐其或有失而不自知也。必稽于众。若人之言是。则必舍己而从之。其无我如此。不自圣如此。此岂非可法者乎。夫圣人。尚或不能无失。况凡人有失。固所必然也。故其言是则固可喜也。虽其不是者。亦当恕而容之。不可罪之也。要使人人各得尽其所怀。而无所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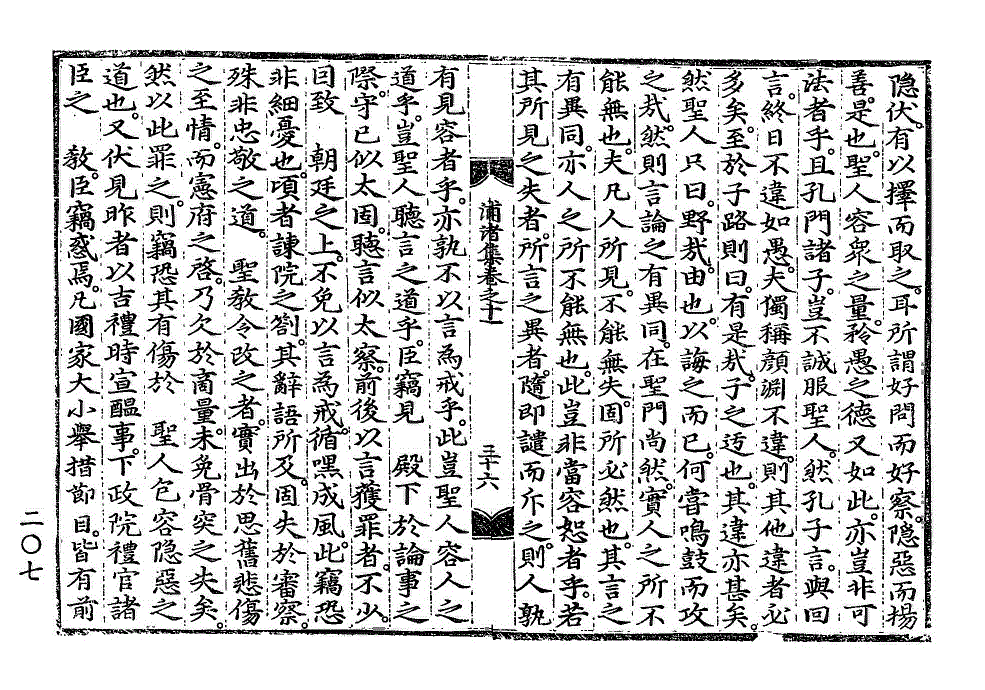 隐伏。有以择而取之耳。所谓好问而好察。隐恶而扬善。是也。圣人容众之量。矜愚之德又如此。亦岂非可法者乎。且孔门诸子。岂不诚服圣人。然孔子言。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夫独称颜渊不违。则其他违者必多矣。至于子路则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其违亦甚矣。然圣人只曰。野哉。由也。以诲之而已。何尝鸣鼓而攻之哉。然则言论之有异同。在圣门尚然。实人之所不能无也。夫凡人所见。不能无失。固所必然也。其言之有异同。亦人之所不能无也。此岂非当容恕者乎。若其所见之失者。所言之异者。随即谴而斥之。则人孰有见容者乎。亦孰不以言为戒乎。此岂圣人容人之道乎。岂圣人听言之道乎。臣窃见 殿下于论事之际。守己似太固。听言似太察。前后以言获罪者。不少。因致 朝廷之上。不免以言为戒。循默成风。此窃恐非细忧也。顷者谏院之劄。其辞语所及。固失于审察。殊非忠敬之道。 圣教令改之者。实出于思旧悲伤之至情。而宪府之启。乃欠于商量。未免骨突之失矣。然以此罪之。则窃恐其有伤于 圣人包容隐恶之道也。又伏见昨者以吉礼时宣酝事。下政院礼官诸臣之 教。臣窃惑焉。凡国家大小举措节目。皆有前
隐伏。有以择而取之耳。所谓好问而好察。隐恶而扬善。是也。圣人容众之量。矜愚之德又如此。亦岂非可法者乎。且孔门诸子。岂不诚服圣人。然孔子言。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夫独称颜渊不违。则其他违者必多矣。至于子路则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其违亦甚矣。然圣人只曰。野哉。由也。以诲之而已。何尝鸣鼓而攻之哉。然则言论之有异同。在圣门尚然。实人之所不能无也。夫凡人所见。不能无失。固所必然也。其言之有异同。亦人之所不能无也。此岂非当容恕者乎。若其所见之失者。所言之异者。随即谴而斥之。则人孰有见容者乎。亦孰不以言为戒乎。此岂圣人容人之道乎。岂圣人听言之道乎。臣窃见 殿下于论事之际。守己似太固。听言似太察。前后以言获罪者。不少。因致 朝廷之上。不免以言为戒。循默成风。此窃恐非细忧也。顷者谏院之劄。其辞语所及。固失于审察。殊非忠敬之道。 圣教令改之者。实出于思旧悲伤之至情。而宪府之启。乃欠于商量。未免骨突之失矣。然以此罪之。则窃恐其有伤于 圣人包容隐恶之道也。又伏见昨者以吉礼时宣酝事。下政院礼官诸臣之 教。臣窃惑焉。凡国家大小举措节目。皆有前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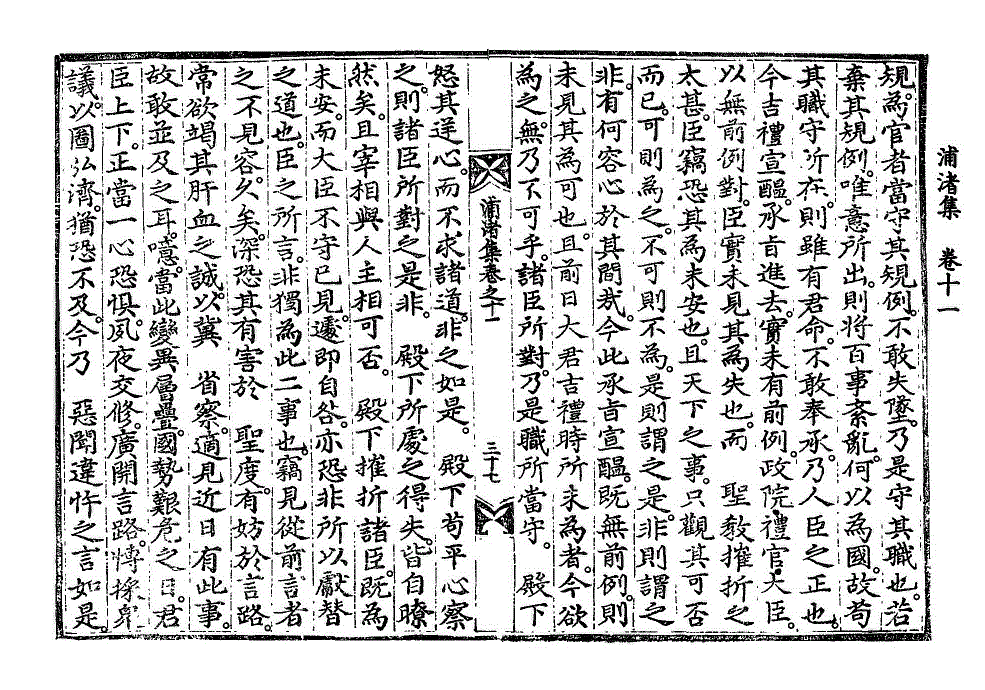 规。为官者当守其规例。不敢失坠。乃是守其职也。若弃其规例。唯意所出。则将百事紊乱。何以为国。故苟其职守所在。则虽有君命。不敢奉承。乃人臣之正也。今吉礼宣酝。承旨进去。实未有前例。政院,礼官,大臣。以无前例对。臣实未见其为失也。而 圣教摧折之太甚。臣窃恐其为未安也。且天下之事。只观其可否而已。可则为之。不可则不为。是则谓之是。非则谓之非。有何容心于其间哉。今此承旨宣酝。既无前例。则未见其为可也。且前日大君吉礼时所未为者。今欲为之。无乃不可乎。诸臣所对。乃是职所当守。 殿下怒其逆心。而不求诸道。非之如是。 殿下苟平心察之。则诸臣所对之是非。 殿下所处之得失。皆自暸然矣。且宰相与人主相可否。 殿下摧折诸臣。既为未安。而大臣不守己见。遽即自咎。亦恐非所以献替之道也。臣之所言。非独为此二事也。窃见从前言者之不见容。久矣。深恐其有害于 圣度。有妨于言路。常欲竭其肝血之诚。以冀 省察。适见近日有此事。故敢并及之耳。噫。当此变异层叠。国势艰危之日。君臣上下。正当一心恐惧。夙夜交修。广开言路。博采众议。以图弘济。犹恐不及。今乃 恶闻违忤之言如是。
规。为官者当守其规例。不敢失坠。乃是守其职也。若弃其规例。唯意所出。则将百事紊乱。何以为国。故苟其职守所在。则虽有君命。不敢奉承。乃人臣之正也。今吉礼宣酝。承旨进去。实未有前例。政院,礼官,大臣。以无前例对。臣实未见其为失也。而 圣教摧折之太甚。臣窃恐其为未安也。且天下之事。只观其可否而已。可则为之。不可则不为。是则谓之是。非则谓之非。有何容心于其间哉。今此承旨宣酝。既无前例。则未见其为可也。且前日大君吉礼时所未为者。今欲为之。无乃不可乎。诸臣所对。乃是职所当守。 殿下怒其逆心。而不求诸道。非之如是。 殿下苟平心察之。则诸臣所对之是非。 殿下所处之得失。皆自暸然矣。且宰相与人主相可否。 殿下摧折诸臣。既为未安。而大臣不守己见。遽即自咎。亦恐非所以献替之道也。臣之所言。非独为此二事也。窃见从前言者之不见容。久矣。深恐其有害于 圣度。有妨于言路。常欲竭其肝血之诚。以冀 省察。适见近日有此事。故敢并及之耳。噫。当此变异层叠。国势艰危之日。君臣上下。正当一心恐惧。夙夜交修。广开言路。博采众议。以图弘济。犹恐不及。今乃 恶闻违忤之言如是。浦渚先生集卷之十一 第 2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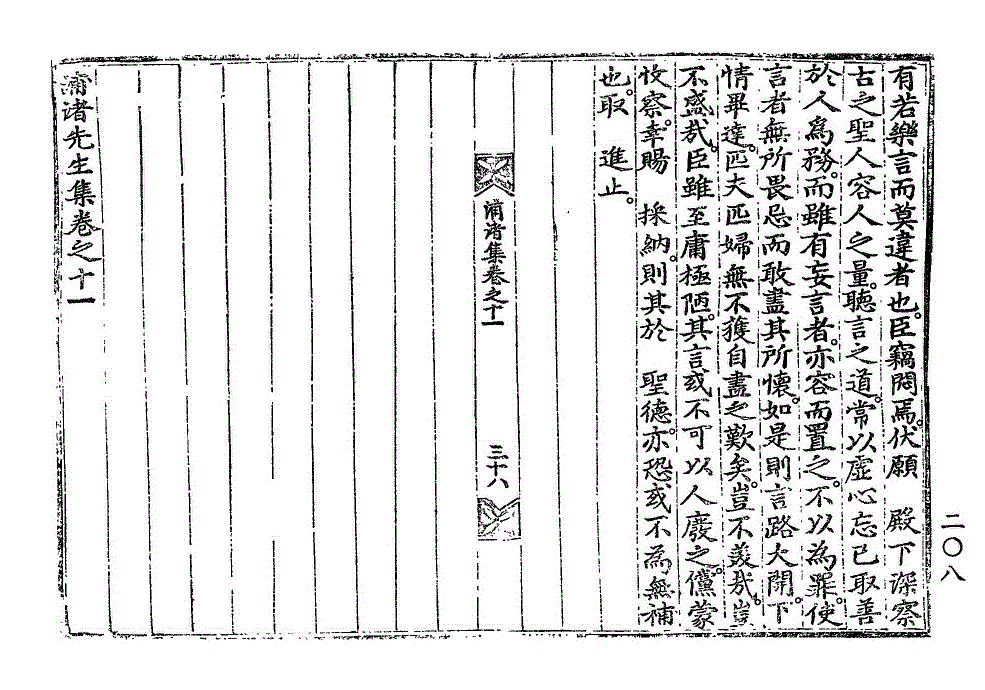 有若乐言而莫违者也。臣窃闷焉。伏愿 殿下深察古之圣人容人之量。听言之道。常以虚心忘己取善于人为务。而虽有妄言者。亦容而置之。不以为罪。使言者无所畏忌而敢尽其所怀。如是则言路大开。下情毕达。匹夫匹妇无不获自尽之叹矣。岂不美哉。岂不盛哉。臣虽至庸极陋。其言或不可以人废之。傥蒙收察。幸赐 采纳。则其于 圣德。亦恐或不为无补也。取 进止。
有若乐言而莫违者也。臣窃闷焉。伏愿 殿下深察古之圣人容人之量。听言之道。常以虚心忘己取善于人为务。而虽有妄言者。亦容而置之。不以为罪。使言者无所畏忌而敢尽其所怀。如是则言路大开。下情毕达。匹夫匹妇无不获自尽之叹矣。岂不美哉。岂不盛哉。臣虽至庸极陋。其言或不可以人废之。傥蒙收察。幸赐 采纳。则其于 圣德。亦恐或不为无补也。取 进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