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x 页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劄(八首)
劄(八首)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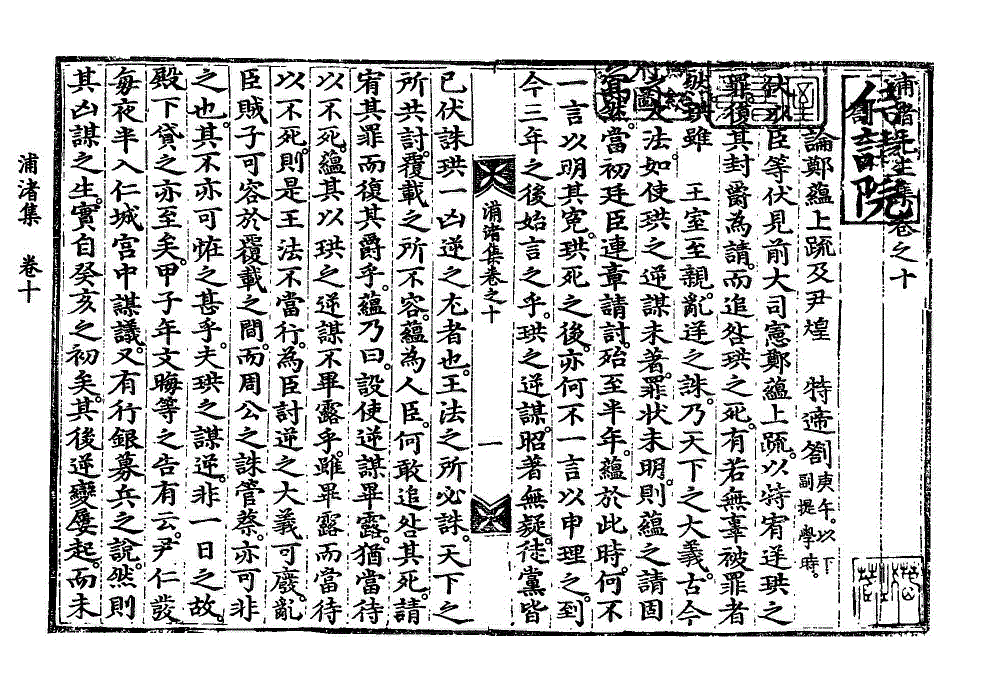 论郑蕴上疏及尹煌 特递劄(庚午。以下副提学时。)
论郑蕴上疏及尹煌 特递劄(庚午。以下副提学时。)伏以臣等伏见前大司宪郑蕴上疏。以特宥逆珙之罪。复其封爵为请。而追咎珙之死。有若无辜被罪者然。珙虽 王室至亲。乱逆之诛。乃天下之大义。古今之大法。如使珙之逆谋未著。罪状未明。则蕴之请固宜然。当初廷臣连章请讨。殆至半年。蕴于此时。何不一言以明其冤。珙死之后。亦何不一言以申理之。到今三年之后始言之乎。珙之逆谋。昭著无疑。徒党皆已伏诛珙一凶逆之尤者也。王法之所必诛。天下之所共讨。覆载之所不容。蕴为人臣。何敢追咎其死。请宥其罪而复其爵乎。蕴乃曰。设使逆谋毕露。犹当待以不死。蕴其以珙之逆谋不毕露乎。虽毕露而当待以不死。则是王法不当行。为臣讨逆之大义可废。乱臣贼子可容于覆载之间。而周公之诛管蔡。亦可非之也。其不亦可怪之甚乎。夫珙之谋逆。非一日之故。殿下贷之亦至矣。甲子年文晦等之告有云。尹仁发每夜半入仁城宫中谋议。又有行银募兵之说。然则其凶谋之生。实自癸亥之初矣。其后逆变屡起。而未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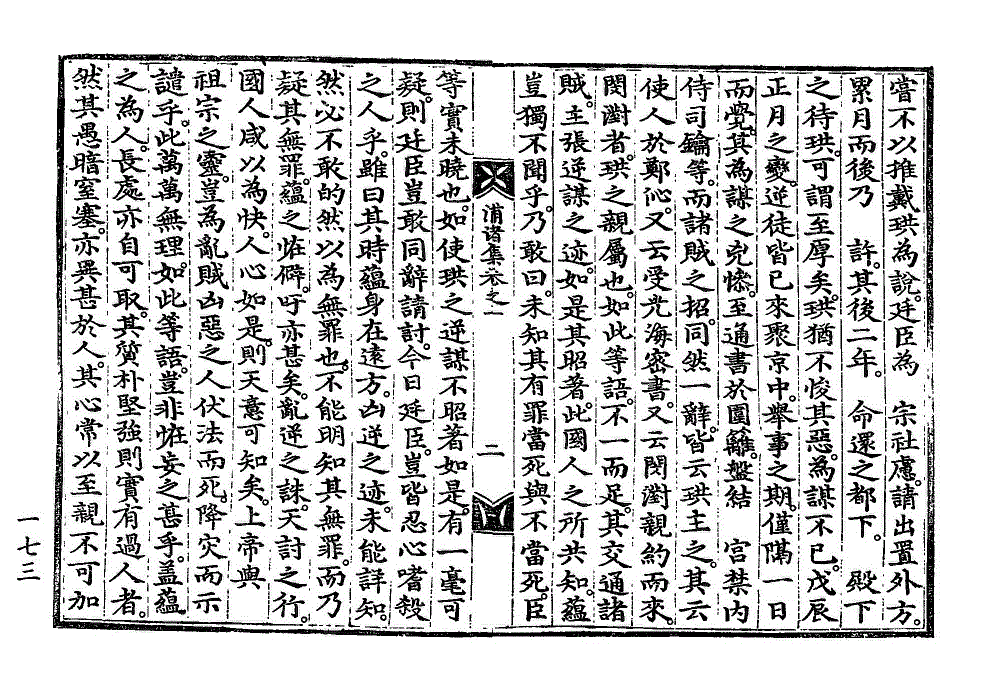 尝不以推戴珙为说。廷臣为 宗社虑。请出置外方。累月而后乃 许。其后二年。 命还之都下。 殿下之待珙。可谓至厚矣。珙犹不悛其恶。为谋不已。戊辰正月之变。逆徒皆已来聚京中。举事之期。仅隔一日而觉。其为谋之凶惨。至通书于围篱。盘结 宫禁内侍司钥等。而诸贼之招。同然一辞。皆云珙主之。其云使人于郑沁。又云受光海密书。又云闵濧亲约而来。闵濧者。珙之亲属也。如此等语。不一而足。其交通诸贼。主张逆谋之迹。如是其昭著。此国人之所共知。蕴岂独不闻乎。乃敢曰。未知其有罪当死与不当死。臣等实未晓也。如使珙之逆谋不昭著如是。有一毫可疑。则廷臣岂敢同辞请讨。今日廷臣。岂皆忍心嗜杀之人乎。虽曰其时蕴身在远方。凶逆之迹。未能详知。然必不敢的然以为无罪也。不能明知其无罪。而乃疑其无罪。蕴之怪僻。吁亦甚矣。乱逆之诛。天讨之行。国人咸以为快。人心如是。则天意可知矣。上帝与 祖宗之灵。岂为乱贼凶恶之人伏法而死。降灾而示谴乎。此万万无理。如此等语。岂非怪妄之甚乎。盖蕴之为人。长处亦自可取。其质朴坚强则实有过人者。然其愚暗窒塞。亦异甚于人。其心常以至亲不可加
尝不以推戴珙为说。廷臣为 宗社虑。请出置外方。累月而后乃 许。其后二年。 命还之都下。 殿下之待珙。可谓至厚矣。珙犹不悛其恶。为谋不已。戊辰正月之变。逆徒皆已来聚京中。举事之期。仅隔一日而觉。其为谋之凶惨。至通书于围篱。盘结 宫禁内侍司钥等。而诸贼之招。同然一辞。皆云珙主之。其云使人于郑沁。又云受光海密书。又云闵濧亲约而来。闵濧者。珙之亲属也。如此等语。不一而足。其交通诸贼。主张逆谋之迹。如是其昭著。此国人之所共知。蕴岂独不闻乎。乃敢曰。未知其有罪当死与不当死。臣等实未晓也。如使珙之逆谋不昭著如是。有一毫可疑。则廷臣岂敢同辞请讨。今日廷臣。岂皆忍心嗜杀之人乎。虽曰其时蕴身在远方。凶逆之迹。未能详知。然必不敢的然以为无罪也。不能明知其无罪。而乃疑其无罪。蕴之怪僻。吁亦甚矣。乱逆之诛。天讨之行。国人咸以为快。人心如是。则天意可知矣。上帝与 祖宗之灵。岂为乱贼凶恶之人伏法而死。降灾而示谴乎。此万万无理。如此等语。岂非怪妄之甚乎。盖蕴之为人。长处亦自可取。其质朴坚强则实有过人者。然其愚暗窒塞。亦异甚于人。其心常以至亲不可加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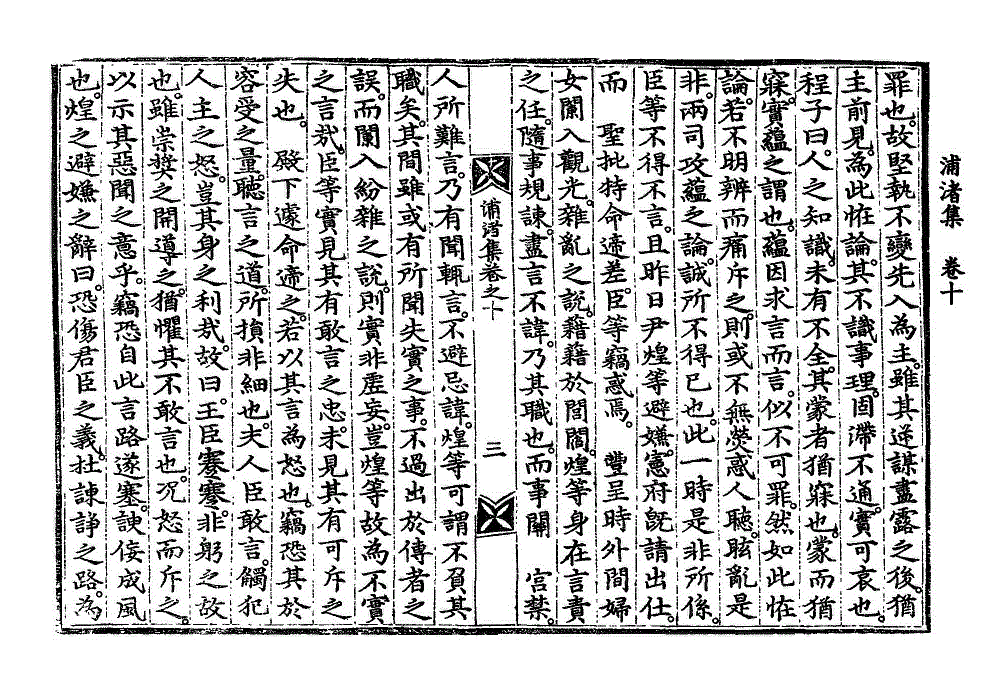 罪也。故坚执不变先入为主。虽其逆谋尽露之后。犹主前见。为此怪论。其不识事理。固滞不通。实可哀也。程子曰。人之知识。未有不全。其蒙者犹寐也。蒙而犹寐。实蕴之谓也。蕴因求言而言。似不可罪。然如此怪论。若不明辨而痛斥之。则或不无荧惑人听。眩乱是非。两司攻蕴之论。诚所不得已也。此一时是非所系。臣等不得不言。且昨日尹煌等避嫌。宪府既请出仕。而 圣批特命递差。臣等窃惑焉。 丰呈时外间妇女阑入观光。杂乱之说。藉藉于闾阎。煌等身在言责之任。随事规谏。尽言不讳。乃其职也。而事关 宫禁。人所难言。乃有闻辄言。不避忌讳。煌等可谓不负其职矣。其间虽或有所闻失实之事。不过出于传者之误。而阑入纷杂之说。则实非虚妄。岂煌等故为不实之言哉。臣等实见其有敢言之忠。未见其有可斥之失也。 殿下遽命递之。若以其言为怒也。窃恐其于容受之量。听言之道。所损非细也。夫人臣敢言。触犯人主之怒。岂其身之利哉。故曰。王臣蹇蹇。非躬之故也。虽崇奖之开导之。犹惧其不敢言也。况怒而斥之。以示其恶闻之意乎。窃恐自此言路遂塞。谀佞成风也。煌之避嫌之辞曰。恐伤君臣之义。杜谏诤之路。为
罪也。故坚执不变先入为主。虽其逆谋尽露之后。犹主前见。为此怪论。其不识事理。固滞不通。实可哀也。程子曰。人之知识。未有不全。其蒙者犹寐也。蒙而犹寐。实蕴之谓也。蕴因求言而言。似不可罪。然如此怪论。若不明辨而痛斥之。则或不无荧惑人听。眩乱是非。两司攻蕴之论。诚所不得已也。此一时是非所系。臣等不得不言。且昨日尹煌等避嫌。宪府既请出仕。而 圣批特命递差。臣等窃惑焉。 丰呈时外间妇女阑入观光。杂乱之说。藉藉于闾阎。煌等身在言责之任。随事规谏。尽言不讳。乃其职也。而事关 宫禁。人所难言。乃有闻辄言。不避忌讳。煌等可谓不负其职矣。其间虽或有所闻失实之事。不过出于传者之误。而阑入纷杂之说。则实非虚妄。岂煌等故为不实之言哉。臣等实见其有敢言之忠。未见其有可斥之失也。 殿下遽命递之。若以其言为怒也。窃恐其于容受之量。听言之道。所损非细也。夫人臣敢言。触犯人主之怒。岂其身之利哉。故曰。王臣蹇蹇。非躬之故也。虽崇奖之开导之。犹惧其不敢言也。况怒而斥之。以示其恶闻之意乎。窃恐自此言路遂塞。谀佞成风也。煌之避嫌之辞曰。恐伤君臣之义。杜谏诤之路。为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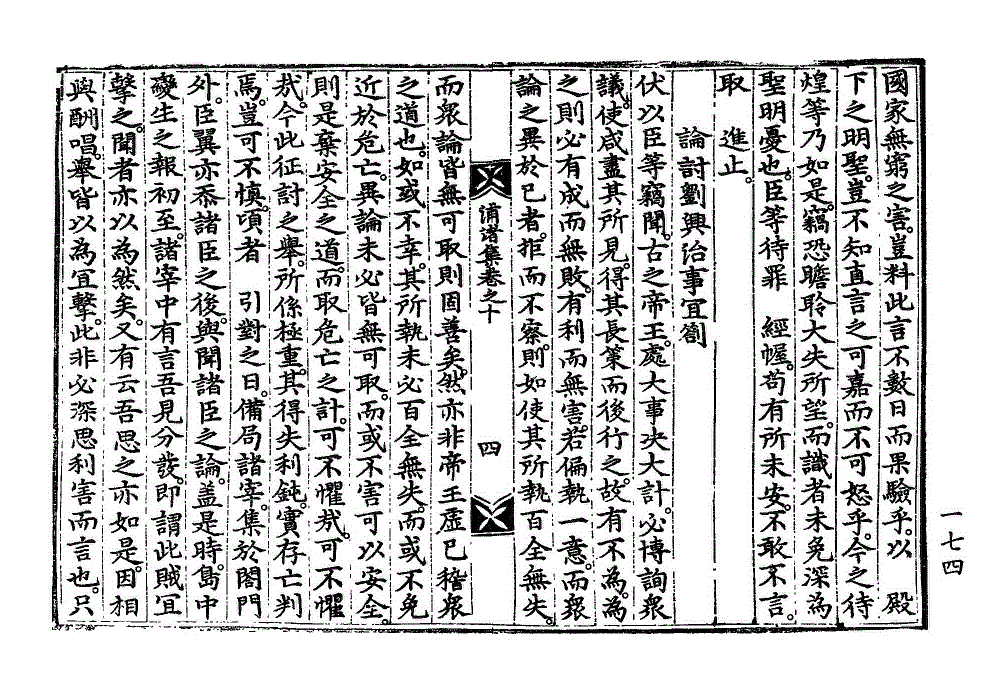 国家无穷之害。岂料此言不数日而果验乎。以 殿下之明圣。岂不知直言之可嘉而不可怒乎。今之待煌等乃如是。窃恐瞻聆大失所望。而识者未免深为圣明忧也。臣等待罪 经幄。苟有所未安。不敢不言。取 进止。
国家无穷之害。岂料此言不数日而果验乎。以 殿下之明圣。岂不知直言之可嘉而不可怒乎。今之待煌等乃如是。窃恐瞻聆大失所望。而识者未免深为圣明忧也。臣等待罪 经幄。苟有所未安。不敢不言。取 进止。论讨刘兴治事宜劄
伏以臣等窃闻。古之帝王。处大事决大计。必博询众议。使咸尽其所见。得其长策而后行之。故有不为。为之则必有成而无败。有利而无害。若偏执一意。而众论之异于己者。拒而不察。则如使其所执百全无失。而众论皆无可取则固善矣。然亦非帝王虚己稽众之道也。如或不幸。其所执未必百全无失。而或不免近于危亡。异论未必皆无可取。而或不害可以安全。则是弃安全之道。而取危亡之计。可不惧哉。可不惧哉。今此征讨之举。所系极重。其得失利钝。实存亡判焉。岂可不慎。顷者 引对之日。备局诸宰。集于閤门外。臣翼亦忝诸臣之后。与闻诸臣之论。盖是时。岛中变生之报初至。诸宰中有言吾见分发。即谓此贼宜击之。闻者亦以为然矣。又有云吾思之亦如是。因相与酬唱。举皆以为宜击。此非必深思利害而言也。只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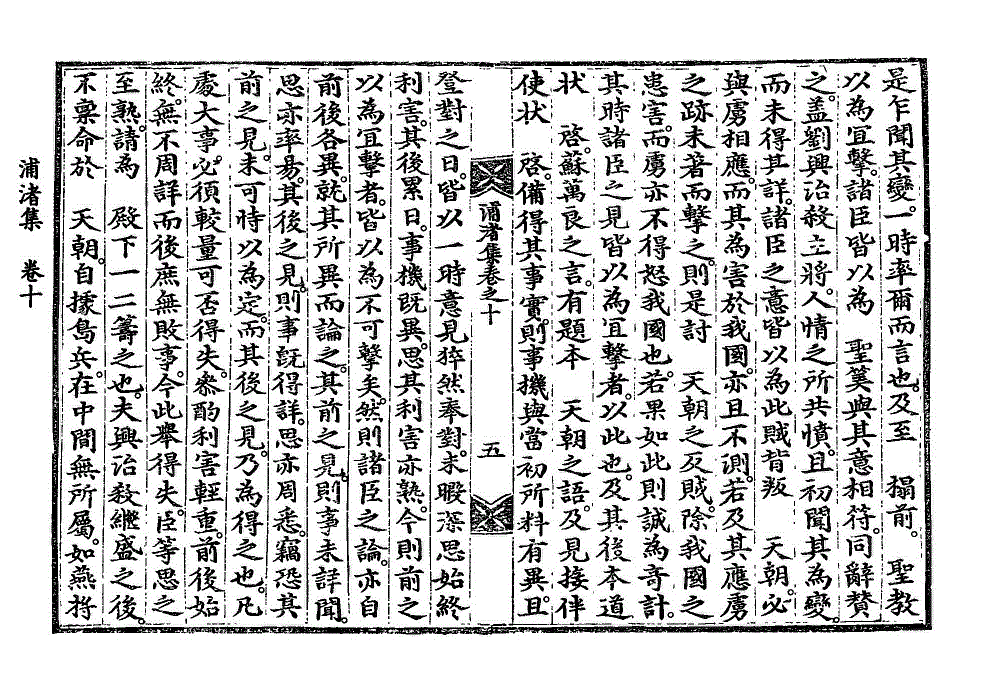 是乍闻其变。一时率尔而言也。及至 榻前。 圣教以为宜击。诸臣皆以为 圣算与其意相符。同辞赞之。盖刘兴治杀主将。人情之所共愤。且初闻其为变。而未得其详。诸臣之意皆以为此贼背叛 天朝。必与虏相应。而其为害于我国。亦且不测。若及其应虏之迹未著而击之。则是讨 天朝之反贼。除我国之患害。而虏亦不得怒我国也。若果如此则诚为奇计。其时诸臣之见皆以为宜击者。以此也。及其后本道状 启。苏万良之言。有题本 天朝之语。及见接伴使状 启。备得其事实。则事机与当初所料有异。且登对之日。皆以一时意见猝然奉对。未暇深思始终利害。其后累日。事机既异。思其利害亦熟。今则前之以为宜击者。皆以为不可击矣。然则诸臣之论。亦自前后各异。就其所异而论之。其前之见。则事未详闻。思亦率易。其后之见。则事既得详。思亦周悉。窃恐其前之见。未可恃以为定。而其后之见。乃为得之也。凡处大事。必须较量可否得失。参酌利害轻重。前后始终。无不周详而后庶无败事。今此举得失。臣等思之至熟。请为 殿下一二筹之也。夫兴治杀继盛之后。不禀命于 天朝。自据岛兵。在中间无所属。如燕将
是乍闻其变。一时率尔而言也。及至 榻前。 圣教以为宜击。诸臣皆以为 圣算与其意相符。同辞赞之。盖刘兴治杀主将。人情之所共愤。且初闻其为变。而未得其详。诸臣之意皆以为此贼背叛 天朝。必与虏相应。而其为害于我国。亦且不测。若及其应虏之迹未著而击之。则是讨 天朝之反贼。除我国之患害。而虏亦不得怒我国也。若果如此则诚为奇计。其时诸臣之见皆以为宜击者。以此也。及其后本道状 启。苏万良之言。有题本 天朝之语。及见接伴使状 启。备得其事实。则事机与当初所料有异。且登对之日。皆以一时意见猝然奉对。未暇深思始终利害。其后累日。事机既异。思其利害亦熟。今则前之以为宜击者。皆以为不可击矣。然则诸臣之论。亦自前后各异。就其所异而论之。其前之见。则事未详闻。思亦率易。其后之见。则事既得详。思亦周悉。窃恐其前之见。未可恃以为定。而其后之见。乃为得之也。凡处大事。必须较量可否得失。参酌利害轻重。前后始终。无不周详而后庶无败事。今此举得失。臣等思之至熟。请为 殿下一二筹之也。夫兴治杀继盛之后。不禀命于 天朝。自据岛兵。在中间无所属。如燕将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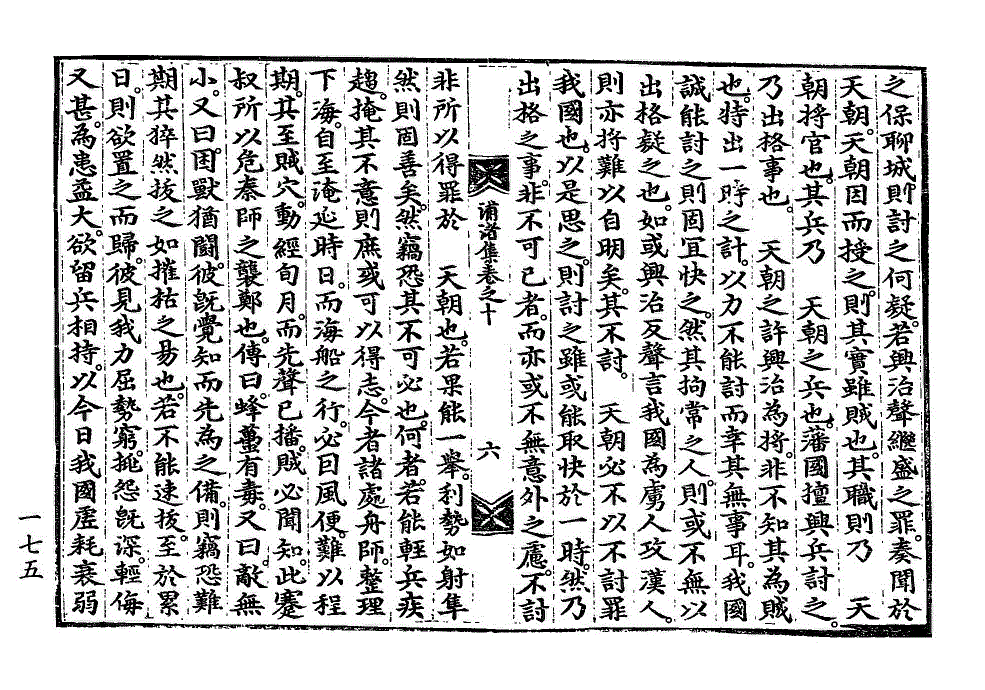 之保聊城。则讨之何疑。若兴治声继盛之罪。奏闻于天朝。天朝因而授之。则其实虽贼也。其职则乃 天朝将官也。其兵乃 天朝之兵也。藩国擅兴兵讨之。乃出格事也。 天朝之许兴治为将。非不知其为贼也。特出一时之计。以力不能讨而幸其无事耳。我国诚能讨之则固宜快之。然其拘常之人。则或不无以出格疑之也。如或兴治反声言我国为虏人攻汉人。则亦将难以自明矣。其不讨。 天朝必不以不讨罪我国也。以是思之。则讨之虽或能取快于一时。然乃出格之事。非不可已者。而亦或不无意外之虑。不讨非所以得罪于 天朝也。若果能一举。利势如射隼然则固善矣。然窃恐其不可必也。何者。若能轻兵疾趋。掩其不意则庶或可以得志。今者诸处舟师。整理下海。自至淹延时日。而海船之行。必因风便。难以程期。其至贼穴。动经旬月。而先声已播。贼必闻知。此蹇叔所以危秦师之袭郑也。传曰。蜂虿有毒。又曰。敌无小。又曰。困兽犹斗。彼既觉知而先为之备。则窃恐难期其猝然拔之如摧枯之易也。若不能速拔。至于累日。则欲置之而归。彼见我力屈势穷。挑怨既深。轻侮又甚。为患益大。欲留兵相持。以今日我国虚耗衰弱
之保聊城。则讨之何疑。若兴治声继盛之罪。奏闻于天朝。天朝因而授之。则其实虽贼也。其职则乃 天朝将官也。其兵乃 天朝之兵也。藩国擅兴兵讨之。乃出格事也。 天朝之许兴治为将。非不知其为贼也。特出一时之计。以力不能讨而幸其无事耳。我国诚能讨之则固宜快之。然其拘常之人。则或不无以出格疑之也。如或兴治反声言我国为虏人攻汉人。则亦将难以自明矣。其不讨。 天朝必不以不讨罪我国也。以是思之。则讨之虽或能取快于一时。然乃出格之事。非不可已者。而亦或不无意外之虑。不讨非所以得罪于 天朝也。若果能一举。利势如射隼然则固善矣。然窃恐其不可必也。何者。若能轻兵疾趋。掩其不意则庶或可以得志。今者诸处舟师。整理下海。自至淹延时日。而海船之行。必因风便。难以程期。其至贼穴。动经旬月。而先声已播。贼必闻知。此蹇叔所以危秦师之袭郑也。传曰。蜂虿有毒。又曰。敌无小。又曰。困兽犹斗。彼既觉知而先为之备。则窃恐难期其猝然拔之如摧枯之易也。若不能速拔。至于累日。则欲置之而归。彼见我力屈势穷。挑怨既深。轻侮又甚。为患益大。欲留兵相持。以今日我国虚耗衰弱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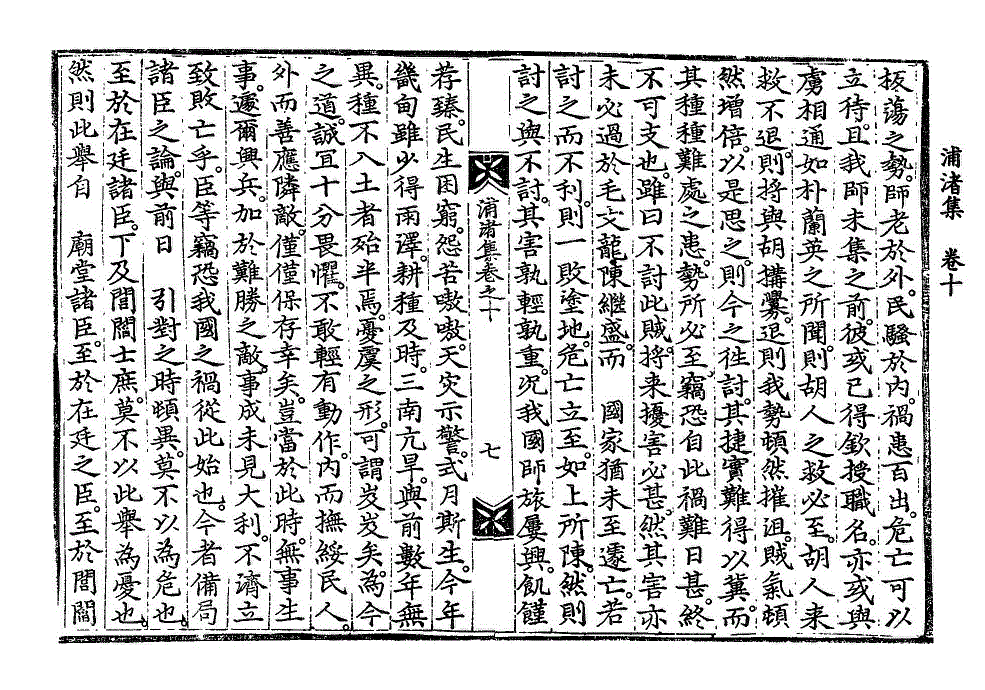 板荡之势。师老于外。民骚于内。祸患百出。危亡可以立待。且我师未集之前。彼或已得钦授职名。亦或与虏相通如朴兰英之所闻。则胡人之救必至。胡人来救不退。则将与胡搆衅。退则我势顿然摧沮。贼气顿然增倍。以是思之。则今之往讨。其捷实难得以冀。而其种种难处之患。势所必至。窃恐自此祸难日甚。终不可支也。虽曰不讨此贼。将来扰害必甚。然其害亦未必过于毛文龙,陈继盛。而 国家犹未至遽亡。若讨之而不利。则一败涂地。危亡立至。如上所陈。然则讨之与不讨。其害孰轻孰重。况我国师旅屡兴。饥馑荐臻。民生困穷。怨苦嗷嗷。天灾示警。式月斯生。今年畿甸虽少得雨泽。耕种及时。三南亢旱。与前数年无异。种不入土者殆半焉。忧虞之形。可谓岌岌矣。为今之道。诚宜十分畏惧。不敢轻有动作。内而抚绥民人。外而善应邻敌。仅仅保存幸矣。岂当于此时。无事生事。遽尔兴兵。加于难胜之敌。事成未见大利。不济立致败亡乎。臣等窃恐我国之祸从此始也。今者备局诸臣之论。与前日 引对之时顿异。莫不以为危也。至于在廷诸臣。下及闾阎士庶。莫不以此举为忧也。然则此举自 庙堂诸臣。至于在廷之臣。至于闾阎
板荡之势。师老于外。民骚于内。祸患百出。危亡可以立待。且我师未集之前。彼或已得钦授职名。亦或与虏相通如朴兰英之所闻。则胡人之救必至。胡人来救不退。则将与胡搆衅。退则我势顿然摧沮。贼气顿然增倍。以是思之。则今之往讨。其捷实难得以冀。而其种种难处之患。势所必至。窃恐自此祸难日甚。终不可支也。虽曰不讨此贼。将来扰害必甚。然其害亦未必过于毛文龙,陈继盛。而 国家犹未至遽亡。若讨之而不利。则一败涂地。危亡立至。如上所陈。然则讨之与不讨。其害孰轻孰重。况我国师旅屡兴。饥馑荐臻。民生困穷。怨苦嗷嗷。天灾示警。式月斯生。今年畿甸虽少得雨泽。耕种及时。三南亢旱。与前数年无异。种不入土者殆半焉。忧虞之形。可谓岌岌矣。为今之道。诚宜十分畏惧。不敢轻有动作。内而抚绥民人。外而善应邻敌。仅仅保存幸矣。岂当于此时。无事生事。遽尔兴兵。加于难胜之敌。事成未见大利。不济立致败亡乎。臣等窃恐我国之祸从此始也。今者备局诸臣之论。与前日 引对之时顿异。莫不以为危也。至于在廷诸臣。下及闾阎士庶。莫不以此举为忧也。然则此举自 庙堂诸臣。至于在廷之臣。至于闾阎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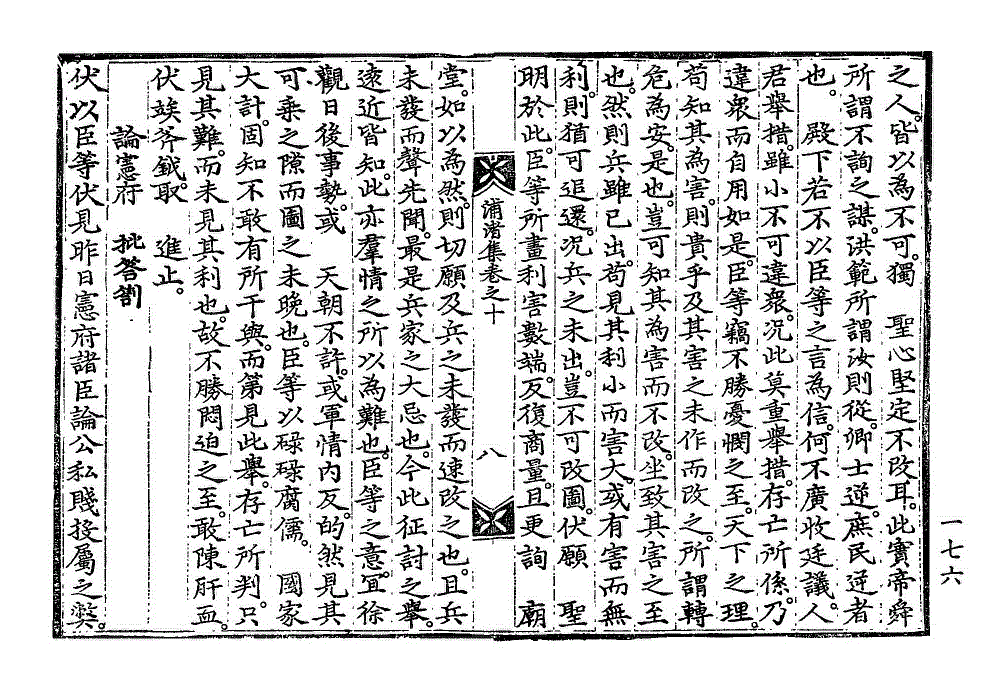 之人。皆以为不可。独 圣心坚定不改耳。此实帝舜所谓不询之谋。洪范所谓汝则从。卿士逆。庶民逆者也。 殿下若不以臣等之言为信。何不广收廷议。人君举措。虽小不可违众。况此莫重举措。存亡所系。乃违众而自用如是。臣等窃不胜忧悯之至。天下之理。苟知其为害。则贵乎及其害之未作而改之。所谓转危为安。是也。岂可知其为害而不改。坐致其害之至也。然则兵虽已出。苟见其利小而害大。或有害而无利。则犹可追还。况兵之未出。岂不可改图。伏愿 圣明于此。臣等所画利害数端。反复商量。且更询 庙堂。如以为然。则切愿及兵之未发而速改之也。且兵未发而声先闻。最是兵家之大忌也。今此征讨之举。远近皆知。此亦群情之所以为难也。臣等之意。宜徐观日后事势。或 天朝不许。或军情内反。的然见其可乘之隙而图之未晚也。臣等以碌碌腐儒。 国家大计。固知不敢有所干与。而第见此举。存亡所判。只见其难。而未见其利也。故不胜闷迫之至。敢陈肝血。伏俟斧钺。取 进止。
之人。皆以为不可。独 圣心坚定不改耳。此实帝舜所谓不询之谋。洪范所谓汝则从。卿士逆。庶民逆者也。 殿下若不以臣等之言为信。何不广收廷议。人君举措。虽小不可违众。况此莫重举措。存亡所系。乃违众而自用如是。臣等窃不胜忧悯之至。天下之理。苟知其为害。则贵乎及其害之未作而改之。所谓转危为安。是也。岂可知其为害而不改。坐致其害之至也。然则兵虽已出。苟见其利小而害大。或有害而无利。则犹可追还。况兵之未出。岂不可改图。伏愿 圣明于此。臣等所画利害数端。反复商量。且更询 庙堂。如以为然。则切愿及兵之未发而速改之也。且兵未发而声先闻。最是兵家之大忌也。今此征讨之举。远近皆知。此亦群情之所以为难也。臣等之意。宜徐观日后事势。或 天朝不许。或军情内反。的然见其可乘之隙而图之未晚也。臣等以碌碌腐儒。 国家大计。固知不敢有所干与。而第见此举。存亡所判。只见其难。而未见其利也。故不胜闷迫之至。敢陈肝血。伏俟斧钺。取 进止。论宪府 批答劄
伏以臣等伏见昨日宪府诸臣论公私贱投属之弊。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77H 页
 而 圣教既使之详论姓名。又斥之以无据与欠正直。显示恶闻之意。臣等窃恐 圣明于台臣之言。或未能深察也。夫我国士民之有奴婢。实财产之大者。其赖以为生业。与土田无异。所贵于治者。使人各保其产业。无相侵夺。此乃所谓絜矩之道也。若不为辨理。任其投属。容其占夺。则夺之者为贪冒不义。不可为俗。被夺者为失业饥寒。怨苦可闷。此大乱之道也。民人之相夺。犹为可恶。为治者固当明辨而深惩之。使无此弊。况以上司衙门。为逋逃之渊薮可乎。又况内需司乃人主之私储。若内需司有容受投属之事。则其何以禁诸司之投属。亦何以禁庶民之相夺乎。此正人心离合。 国家存亡之大机关也。岂非深可惧乎。废朝之政。无事不乱。而此其一也。 反正之后。一反废朝所为。抱冤之人。颇得辨理。民情咸以为快。近年以来。民间颇有此弊复起之语。其奴婢投入。而不得推者。往往有之。至于京外之人。呈 上言者亦多。夫幽远之小民。有不得其所。能自直于州县鲜矣。况 上言之捧。甚为稀罕。遐方之人。能自致于京师。以其言得达于 冕旒者。窃恐十不一二也。盖内奴之役。在于诸役。最为轻歇。故非但私奴之叛主者归
而 圣教既使之详论姓名。又斥之以无据与欠正直。显示恶闻之意。臣等窃恐 圣明于台臣之言。或未能深察也。夫我国士民之有奴婢。实财产之大者。其赖以为生业。与土田无异。所贵于治者。使人各保其产业。无相侵夺。此乃所谓絜矩之道也。若不为辨理。任其投属。容其占夺。则夺之者为贪冒不义。不可为俗。被夺者为失业饥寒。怨苦可闷。此大乱之道也。民人之相夺。犹为可恶。为治者固当明辨而深惩之。使无此弊。况以上司衙门。为逋逃之渊薮可乎。又况内需司乃人主之私储。若内需司有容受投属之事。则其何以禁诸司之投属。亦何以禁庶民之相夺乎。此正人心离合。 国家存亡之大机关也。岂非深可惧乎。废朝之政。无事不乱。而此其一也。 反正之后。一反废朝所为。抱冤之人。颇得辨理。民情咸以为快。近年以来。民间颇有此弊复起之语。其奴婢投入。而不得推者。往往有之。至于京外之人。呈 上言者亦多。夫幽远之小民。有不得其所。能自直于州县鲜矣。况 上言之捧。甚为稀罕。遐方之人。能自致于京师。以其言得达于 冕旒者。窃恐十不一二也。盖内奴之役。在于诸役。最为轻歇。故非但私奴之叛主者归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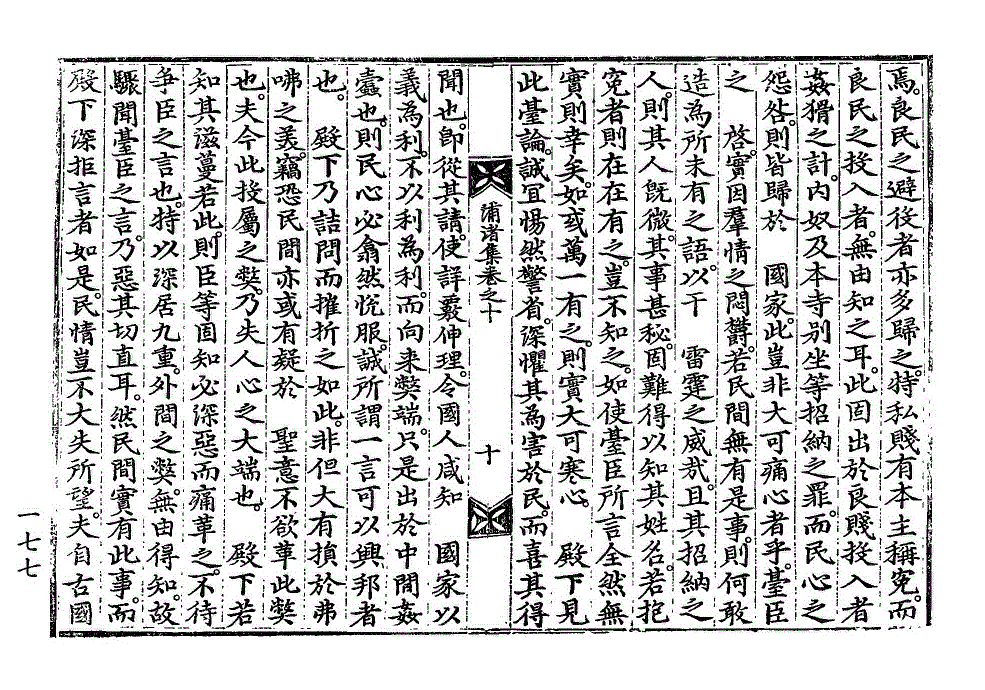 焉。良民之避役者亦多归之。特私贱有本主称冤。而良民之投入者。无由知之耳。此固出于良贱投入者奸猾之计。内奴及本寺别坐等招纳之罪。而民心之怨咎。则皆归于 国家。此岂非大可痛心者乎。台臣之 启。实因群情之闷郁。若民间无有是事。则何敢造为所未有之语。以干 雷霆之威哉。且其招纳之人。则其人既微。其事甚秘。固难得以知其姓名。若抱冤者则在在有之。岂不知之。如使台臣所言全然无实则幸矣。如或万一有之。则实大可寒心。 殿下见此台论。诚宜惕然警省。深惧其为害于民。而喜其得闻也。即从其请。使详覈伸理。令国人咸知 国家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而向来弊端。只是出于中间奸蠹也。则民心必翕然悦服。诚所谓一言可以兴邦者也。 殿下乃诘问而摧折之如此。非但大有损于弗咈之美。窃恐民间亦或有疑于 圣意不欲革此弊也。夫今此投属之弊。乃失人心之大端也。 殿下若知其滋蔓若此。则臣等固知必深恶而痛革之。不待争臣之言也。特以深居九重。外间之弊。无由得知。故骤闻台臣之言。乃恶其切直耳。然民间实有此事。而殿下深拒言者如是。民情岂不大失所望。夫自古国
焉。良民之避役者亦多归之。特私贱有本主称冤。而良民之投入者。无由知之耳。此固出于良贱投入者奸猾之计。内奴及本寺别坐等招纳之罪。而民心之怨咎。则皆归于 国家。此岂非大可痛心者乎。台臣之 启。实因群情之闷郁。若民间无有是事。则何敢造为所未有之语。以干 雷霆之威哉。且其招纳之人。则其人既微。其事甚秘。固难得以知其姓名。若抱冤者则在在有之。岂不知之。如使台臣所言全然无实则幸矣。如或万一有之。则实大可寒心。 殿下见此台论。诚宜惕然警省。深惧其为害于民。而喜其得闻也。即从其请。使详覈伸理。令国人咸知 国家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而向来弊端。只是出于中间奸蠹也。则民心必翕然悦服。诚所谓一言可以兴邦者也。 殿下乃诘问而摧折之如此。非但大有损于弗咈之美。窃恐民间亦或有疑于 圣意不欲革此弊也。夫今此投属之弊。乃失人心之大端也。 殿下若知其滋蔓若此。则臣等固知必深恶而痛革之。不待争臣之言也。特以深居九重。外间之弊。无由得知。故骤闻台臣之言。乃恶其切直耳。然民间实有此事。而殿下深拒言者如是。民情岂不大失所望。夫自古国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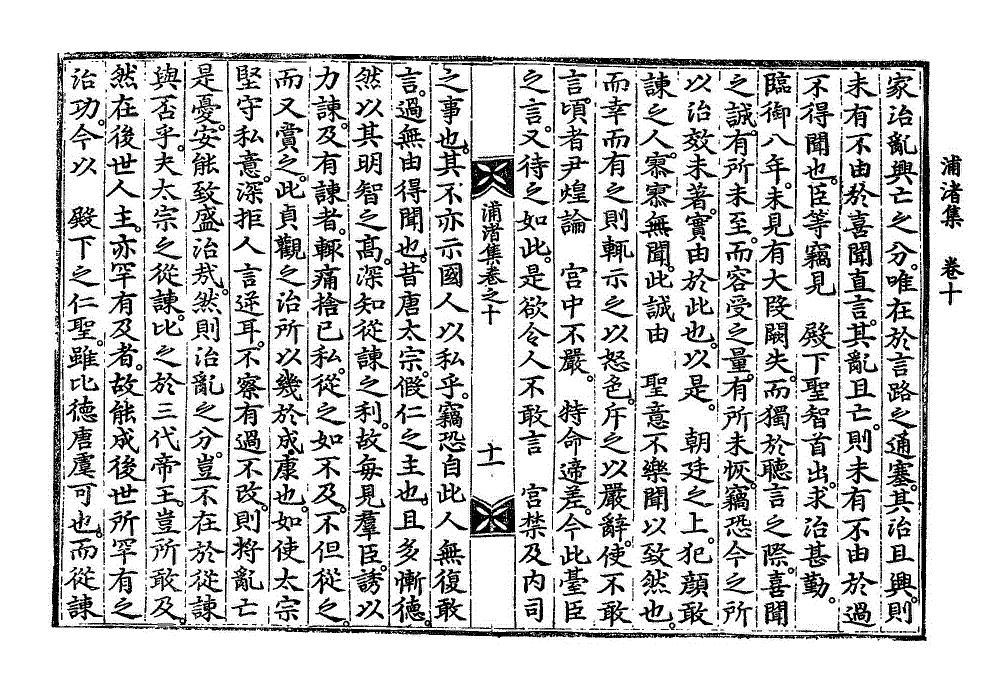 家治乱兴亡之分。唯在于言路之通塞。其治且兴。则未有不由于喜闻直言。其乱且亡。则未有不由于过不得闻也。臣等窃见 殿下圣智首出。求治甚勤。 临御八年。未见有大段阙失。而独于听言之际。喜闻之诚。有所未至。而容受之量。有所未恢。窃恐今之所以治效未著。实由于此也。以是。 朝廷之上。犯颜敢谏之人。寥寥无闻。此诚由 圣意不乐闻以致然也。而幸而有之则辄示之以怒色。斥之以严辞。使不敢言。顷者尹煌论 宫中不严。 特命递差。今此台臣之言。又待之如此。是欲令人不敢言 宫禁及内司之事也。其不亦示国人以私乎。窃恐自此人无复敢言。过无由得闻也。昔唐太宗。假仁之主也。且多惭德。然以其明智之高。深知从谏之利。故每见群臣。诱以力谏。及有谏者。辄痛舍己私。从之如不及。不但从之。而又赏之。此贞观之治所以几于成,康也。如使太宗坚守私意。深拒人言逆耳。不察有过不改。则将乱亡是忧。安能致盛治哉。然则治乱之分。岂不在于从谏与否乎。夫太宗之从谏。比之于三代帝王。岂所敢及。然在后世人主。亦罕有及者。故能成后世所罕有之治功。今以 殿下之仁圣。虽比德唐虞可也。而从谏
家治乱兴亡之分。唯在于言路之通塞。其治且兴。则未有不由于喜闻直言。其乱且亡。则未有不由于过不得闻也。臣等窃见 殿下圣智首出。求治甚勤。 临御八年。未见有大段阙失。而独于听言之际。喜闻之诚。有所未至。而容受之量。有所未恢。窃恐今之所以治效未著。实由于此也。以是。 朝廷之上。犯颜敢谏之人。寥寥无闻。此诚由 圣意不乐闻以致然也。而幸而有之则辄示之以怒色。斥之以严辞。使不敢言。顷者尹煌论 宫中不严。 特命递差。今此台臣之言。又待之如此。是欲令人不敢言 宫禁及内司之事也。其不亦示国人以私乎。窃恐自此人无复敢言。过无由得闻也。昔唐太宗。假仁之主也。且多惭德。然以其明智之高。深知从谏之利。故每见群臣。诱以力谏。及有谏者。辄痛舍己私。从之如不及。不但从之。而又赏之。此贞观之治所以几于成,康也。如使太宗坚守私意。深拒人言逆耳。不察有过不改。则将乱亡是忧。安能致盛治哉。然则治乱之分。岂不在于从谏与否乎。夫太宗之从谏。比之于三代帝王。岂所敢及。然在后世人主。亦罕有及者。故能成后世所罕有之治功。今以 殿下之仁圣。虽比德唐虞可也。而从谏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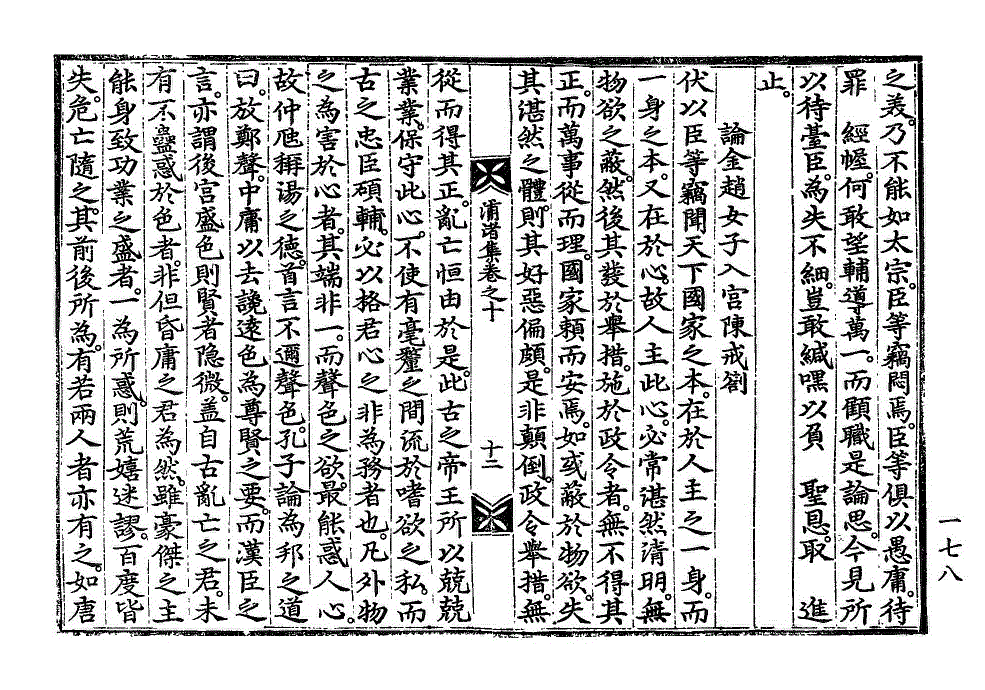 之美。乃不能如太宗。臣等窃闷焉。臣等俱以愚庸。待罪 经幄。何敢望辅导万一。而顾职是论思。今见所以待台臣。为失不细。岂敢缄默以负 圣恩。取 进止。
之美。乃不能如太宗。臣等窃闷焉。臣等俱以愚庸。待罪 经幄。何敢望辅导万一。而顾职是论思。今见所以待台臣。为失不细。岂敢缄默以负 圣恩。取 进止。论金赵女子入宫陈戒劄
伏以臣等窃闻天下国家之本。在于人主之一身。而一身之本。又在于心。故人主此心。必常湛然清明。无物欲之蔽。然后其发于举措。施于政令者。无不得其正。而万事从而理。国家赖而安焉。如或蔽于物欲。失其湛然之体。则其好恶偏颇。是非颠倒。政令举措。无从而得其正。乱亡恒由于是。此古之帝王所以兢兢业业。保守此心。不使有毫釐之间流于嗜欲之私。而古之忠臣硕辅。必以格君心之非为务者也。凡外物之为害于心者。其端非一。而声色之欲。最能惑人心。故仲虺称汤之德。首言不迩声色。孔子论为邦之道曰。放郑声。中庸以去谗远色为尊贤之要。而汉臣之言。亦谓后宫盛色则贤者隐微。盖自古乱亡之君。未有不蛊惑于色者。非但昏庸之君为然。虽豪杰之主能身致功业之盛者。一为所惑。则荒嬉迷谬。百度皆失。危亡随之。其前后所为。有若两人者亦有之。如唐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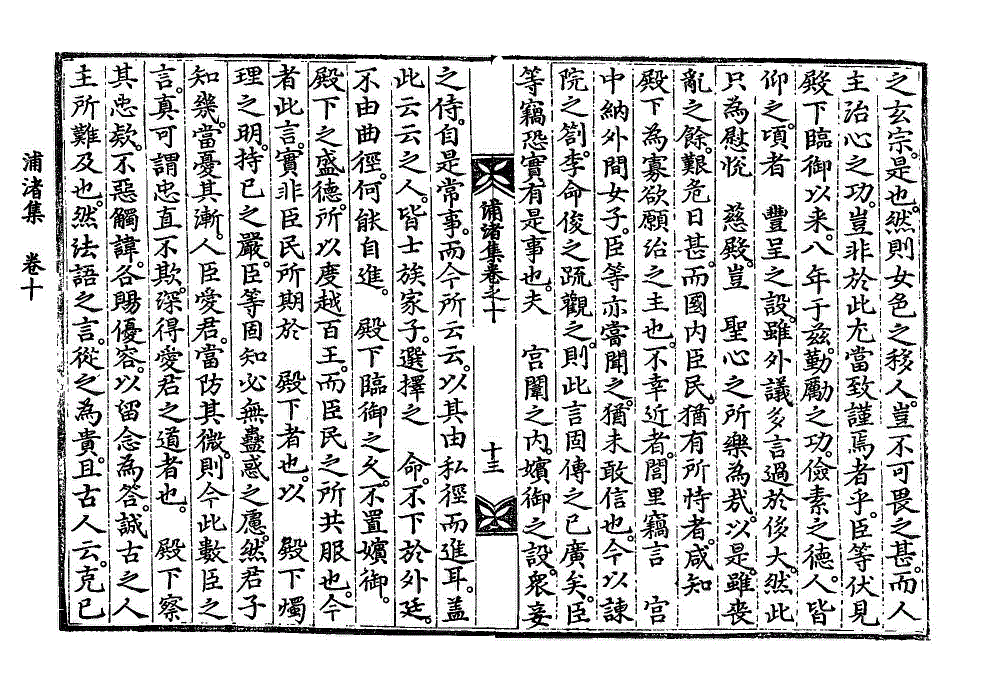 之玄宗。是也。然则女色之移人。岂不可畏之甚。而人主治心之功。岂非于此尤当致谨焉者乎。臣等伏见殿下临御以来。八年于兹。勤励之功。俭素之德。人皆仰之。顷者 丰呈之设。虽外议多言过于侈大。然此只为慰悦 慈殿。岂 圣心之所乐为哉。以是。虽丧乱之馀。艰危日甚。而国内臣民。犹有所恃者。咸知 殿下为寡欲愿治之主也。不幸近者。闾里窃言 宫中纳外间女子。臣等亦尝闻之。犹未敢信也。今以谏院之劄。李命俊之疏观之。则此言固传之已广矣。臣等窃恐实有是事也。夫 宫闱之内。嫔御之设。众妾之侍。自是常事。而今所云云。以其由私径而进耳。盖此云云之人。皆士族家子。选择之 命。不下于外廷。不由曲径。何能自进。 殿下临御之久。不置嫔御。 殿下之盛德。所以度越百王。而臣民之所共服也。今者此言。实非臣民所期于 殿下者也。以 殿下烛理之明。持己之严。臣等固知必无蛊惑之虑。然君子知几。当忧其渐。人臣爱君。当防其微。则今此数臣之言。真可谓忠直不欺。深得爱君之道者也。 殿下察其忠款。不恶触讳。各赐优容。以留念为答。诚古之人主所难及也。然法语之言。从之为贵。且古人云。克己
之玄宗。是也。然则女色之移人。岂不可畏之甚。而人主治心之功。岂非于此尤当致谨焉者乎。臣等伏见殿下临御以来。八年于兹。勤励之功。俭素之德。人皆仰之。顷者 丰呈之设。虽外议多言过于侈大。然此只为慰悦 慈殿。岂 圣心之所乐为哉。以是。虽丧乱之馀。艰危日甚。而国内臣民。犹有所恃者。咸知 殿下为寡欲愿治之主也。不幸近者。闾里窃言 宫中纳外间女子。臣等亦尝闻之。犹未敢信也。今以谏院之劄。李命俊之疏观之。则此言固传之已广矣。臣等窃恐实有是事也。夫 宫闱之内。嫔御之设。众妾之侍。自是常事。而今所云云。以其由私径而进耳。盖此云云之人。皆士族家子。选择之 命。不下于外廷。不由曲径。何能自进。 殿下临御之久。不置嫔御。 殿下之盛德。所以度越百王。而臣民之所共服也。今者此言。实非臣民所期于 殿下者也。以 殿下烛理之明。持己之严。臣等固知必无蛊惑之虑。然君子知几。当忧其渐。人臣爱君。当防其微。则今此数臣之言。真可谓忠直不欺。深得爱君之道者也。 殿下察其忠款。不恶触讳。各赐优容。以留念为答。诚古之人主所难及也。然法语之言。从之为贵。且古人云。克己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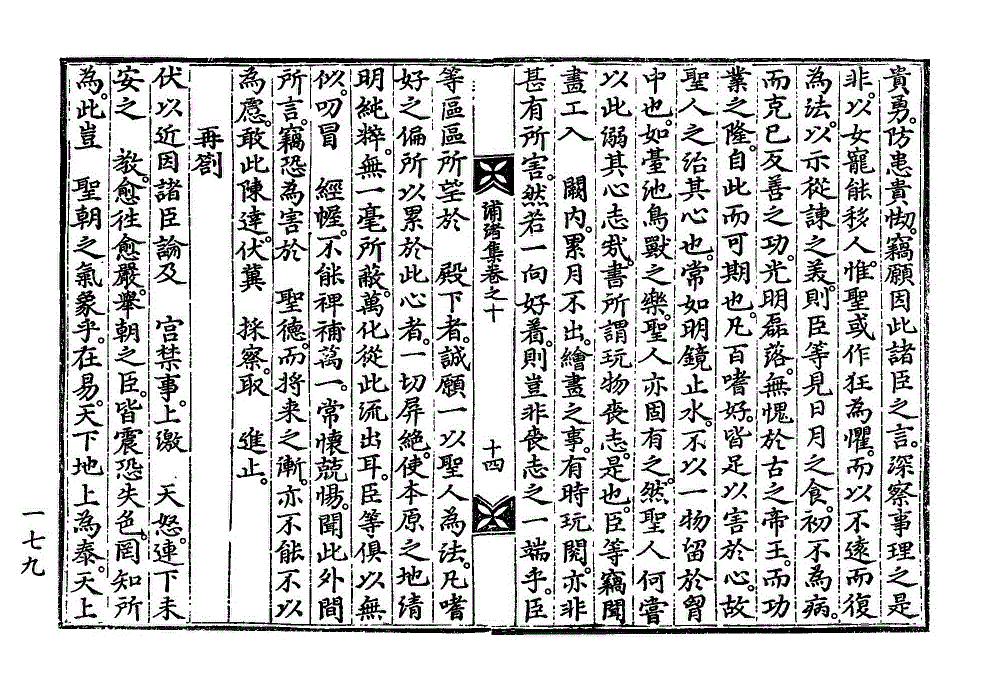 贵勇。防患贵怯。窃愿因此诸臣之言。深察事理之是非。以女宠能移人。惟圣或作狂为惧。而以不远而复为法。以示从谏之美。则臣等见日月之食。初不为病。而克己反善之功。光明磊落。无愧于古之帝王。而功业之隆。自此而可期也。凡百嗜好。皆足以害于心。故圣人之治其心也。常如明镜止水。不以一物留于胸中也。如台池鸟兽之乐。圣人亦固有之。然圣人何尝以此溺其心志哉。书所谓玩物丧志。是也。臣等窃闻画工入 阙内。累月不出。绘画之事。有时玩阅。亦非甚有所害。然若一向好着。则岂非丧志之一端乎。臣等区区所望于 殿下者。诚愿一以圣人为法。凡嗜好之偏所以累于此心者。一切屏绝。使本原之地清明纯粹。无一毫所蔽。万化从此流出耳。臣等俱以无似。叨冒 经幄。不能裨补万一。常怀兢惕。闻此外间所言。窃恐为害于 圣德。而将来之渐。亦不能不以为虑。敢此陈达。伏冀 采察。取 进止。
贵勇。防患贵怯。窃愿因此诸臣之言。深察事理之是非。以女宠能移人。惟圣或作狂为惧。而以不远而复为法。以示从谏之美。则臣等见日月之食。初不为病。而克己反善之功。光明磊落。无愧于古之帝王。而功业之隆。自此而可期也。凡百嗜好。皆足以害于心。故圣人之治其心也。常如明镜止水。不以一物留于胸中也。如台池鸟兽之乐。圣人亦固有之。然圣人何尝以此溺其心志哉。书所谓玩物丧志。是也。臣等窃闻画工入 阙内。累月不出。绘画之事。有时玩阅。亦非甚有所害。然若一向好着。则岂非丧志之一端乎。臣等区区所望于 殿下者。诚愿一以圣人为法。凡嗜好之偏所以累于此心者。一切屏绝。使本原之地清明纯粹。无一毫所蔽。万化从此流出耳。臣等俱以无似。叨冒 经幄。不能裨补万一。常怀兢惕。闻此外间所言。窃恐为害于 圣德。而将来之渐。亦不能不以为虑。敢此陈达。伏冀 采察。取 进止。论金赵女子入宫陈戒劄[再劄]
伏以近因诸臣论及 宫禁事。上激 天怒。连下未安之 教。愈往愈严。举朝之臣。皆震恐失色。罔知所为。此岂 圣朝之气象乎。在易。天下地上为泰。天上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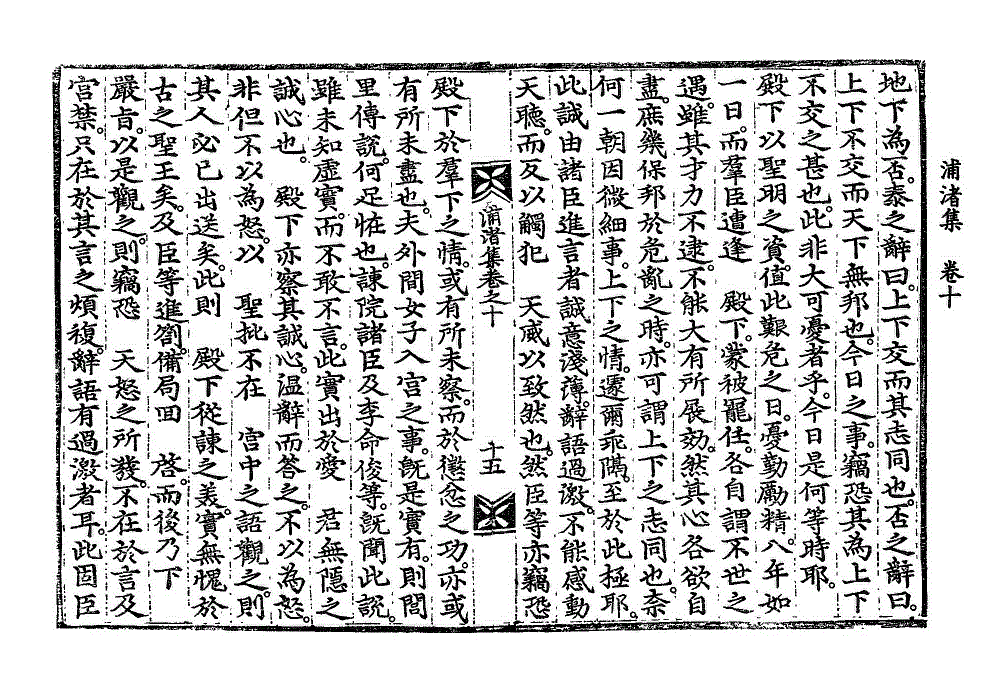 地下为否。泰之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之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今日之事。窃恐其为上下不交之甚也。此非大可忧者乎。今日是何等时耶。 殿下以圣明之资。值此艰危之日。忧勤励精。八年如一日。而群臣遭逢 殿下。蒙被宠任。各自谓不世之遇。虽其才力不逮。不能大有所展效。然其心各欲自尽。庶几保邦于危乱之时。亦可谓上下之志同也。奈何一朝因微细事。上下之情。遽尔乖隔。至于此极耶。此诚由诸臣进言者诚意浅薄。辞语过激。不能感动天听。而反以触犯 天威以致然也。然臣等亦窃恐殿下于群下之情。或有所未察。而于惩忿之功。亦或有所未尽也。夫外间女子入宫之事。既是实有。则闾里传说。何足怪也。谏院诸臣及李命俊等。既闻此说。虽未知虚实。而不敢不言。此实出于爱 君无隐之诚心也。 殿下亦察其诚心。温辞而答之。不以为怒。非但不以为怒。以 圣批不在 宫中之语观之。则其人必已出送矣。此则 殿下从谏之美。实无愧于古之圣王矣。及臣等进劄。备局回 启。而后乃下 严旨。以是观之。则窃恐 天怒之所发。不在于言及宫禁。只在于其言之烦复。辞语有过激者耳。此固臣
地下为否。泰之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之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今日之事。窃恐其为上下不交之甚也。此非大可忧者乎。今日是何等时耶。 殿下以圣明之资。值此艰危之日。忧勤励精。八年如一日。而群臣遭逢 殿下。蒙被宠任。各自谓不世之遇。虽其才力不逮。不能大有所展效。然其心各欲自尽。庶几保邦于危乱之时。亦可谓上下之志同也。奈何一朝因微细事。上下之情。遽尔乖隔。至于此极耶。此诚由诸臣进言者诚意浅薄。辞语过激。不能感动天听。而反以触犯 天威以致然也。然臣等亦窃恐殿下于群下之情。或有所未察。而于惩忿之功。亦或有所未尽也。夫外间女子入宫之事。既是实有。则闾里传说。何足怪也。谏院诸臣及李命俊等。既闻此说。虽未知虚实。而不敢不言。此实出于爱 君无隐之诚心也。 殿下亦察其诚心。温辞而答之。不以为怒。非但不以为怒。以 圣批不在 宫中之语观之。则其人必已出送矣。此则 殿下从谏之美。实无愧于古之圣王矣。及臣等进劄。备局回 启。而后乃下 严旨。以是观之。则窃恐 天怒之所发。不在于言及宫禁。只在于其言之烦复。辞语有过激者耳。此固臣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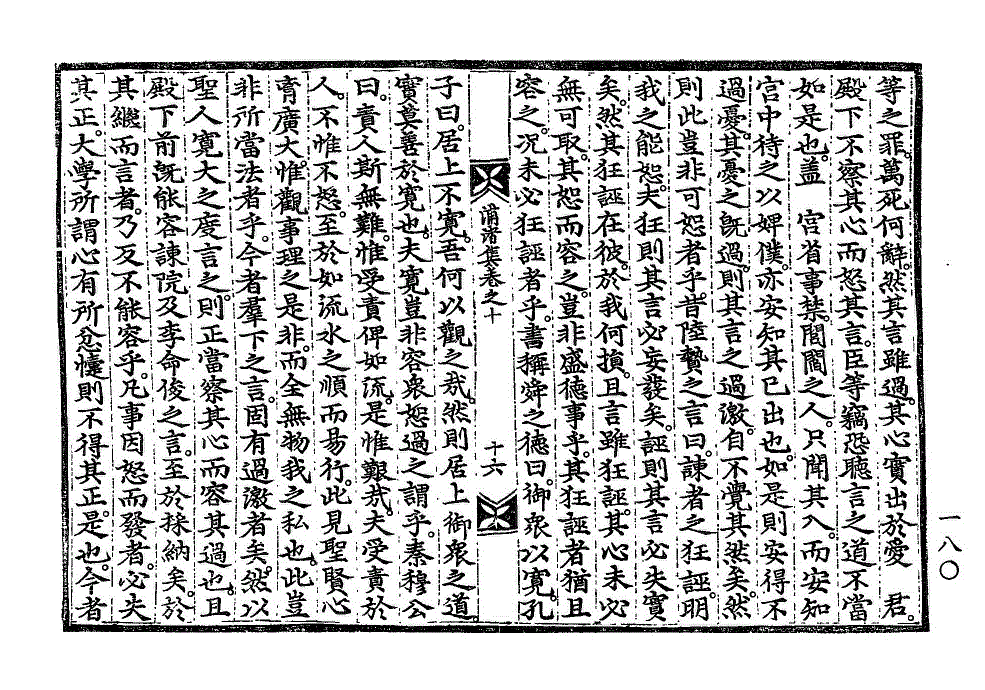 等之罪。万死何辞。然其言虽过。其心实出于爱 君。殿下不察其心而怒其言。臣等窃恐听言之道不当如是也。盖 宫省事禁。闾阎之人。只闻其入。而安知宫中待之以婢仆。亦安知其已出也。如是则安得不过忧。其忧之既过。则其言之过激。自不觉其然矣。然则此岂非可恕者乎。昔陆贽之言曰。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夫狂则其言必妄发矣。诬则其言必失实矣。然其狂诬在彼。于我何损。且言虽狂诬。其心未必无可取。其恕而容之。岂非盛德事乎。其狂诬者犹且容之。况未必狂诬者乎。书称舜之德曰。御众以宽。孔子曰。居上不宽。吾何以观之哉。然则居上御众之道。实莫善于宽也。夫宽岂非容众恕过之谓乎。秦穆公曰。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夫受责于人。不惟不怒。至于如流水之顺而易行。此见圣贤心胸广大。惟观事理之是非。而全无物我之私也。此岂非所当法者乎。今者群下之言。固有过激者矣。然以圣人宽大之度言之。则正当察其心而容其过也。且殿下前既能容谏院及李命俊之言。至于采纳矣。于其继而言者。乃反不能容乎。凡事因怒而发者。必失其正。大学所谓心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是也。今者
等之罪。万死何辞。然其言虽过。其心实出于爱 君。殿下不察其心而怒其言。臣等窃恐听言之道不当如是也。盖 宫省事禁。闾阎之人。只闻其入。而安知宫中待之以婢仆。亦安知其已出也。如是则安得不过忧。其忧之既过。则其言之过激。自不觉其然矣。然则此岂非可恕者乎。昔陆贽之言曰。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夫狂则其言必妄发矣。诬则其言必失实矣。然其狂诬在彼。于我何损。且言虽狂诬。其心未必无可取。其恕而容之。岂非盛德事乎。其狂诬者犹且容之。况未必狂诬者乎。书称舜之德曰。御众以宽。孔子曰。居上不宽。吾何以观之哉。然则居上御众之道。实莫善于宽也。夫宽岂非容众恕过之谓乎。秦穆公曰。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夫受责于人。不惟不怒。至于如流水之顺而易行。此见圣贤心胸广大。惟观事理之是非。而全无物我之私也。此岂非所当法者乎。今者群下之言。固有过激者矣。然以圣人宽大之度言之。则正当察其心而容其过也。且殿下前既能容谏院及李命俊之言。至于采纳矣。于其继而言者。乃反不能容乎。凡事因怒而发者。必失其正。大学所谓心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是也。今者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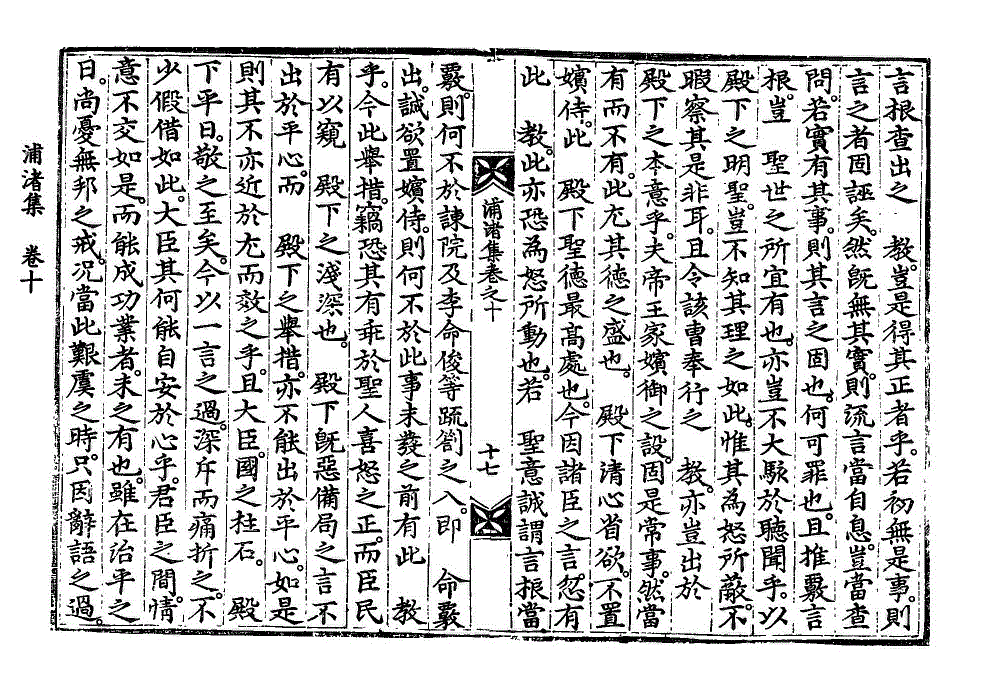 言根查出之 教。岂是得其正者乎。若初无是事。则言之者固诬矣。然既无其实。则流言当自息。岂当查问。若实有其事。则其言之固也。何可罪也。且推覈言根。岂 圣世之所宜有也。亦岂不大骇于听闻乎。以殿下之明圣。岂不知其理之如此。惟其为怒所蔽。不暇察其是非耳。且令该曹奉行之 教。亦岂出于 殿下之本意乎。夫帝王家嫔御之设。固是常事。然当有而不有。此尤其德之盛也。 殿下清心省欲。不置嫔侍。此 殿下圣德最高处也。今因诸臣之言。忽有此 教。此亦恐为怒所动也。若 圣意诚谓言根当覈。则何不于谏院及李命俊等疏劄之入。即 命覈出。诚欲置嫔侍。则何不于此事未发之前有此 教乎。今此举措。窃恐其有乖于圣人喜怒之正。而臣民有以窥 殿下之浅深也。 殿下既恶备局之言不出于平心。而 殿下之举措。亦不能出于平心。如是则其不亦近于尤而效之乎。且大臣。国之柱石。 殿下平日。敬之至矣。今以一言之过。深斥而痛折之。不少假借如此。大臣其何能自安于心乎。君臣之间。情意不交如是。而能成功业者。未之有也。虽在治平之日。尚忧无邦之戒。况当此艰虞之时。只因辞语之过。
言根查出之 教。岂是得其正者乎。若初无是事。则言之者固诬矣。然既无其实。则流言当自息。岂当查问。若实有其事。则其言之固也。何可罪也。且推覈言根。岂 圣世之所宜有也。亦岂不大骇于听闻乎。以殿下之明圣。岂不知其理之如此。惟其为怒所蔽。不暇察其是非耳。且令该曹奉行之 教。亦岂出于 殿下之本意乎。夫帝王家嫔御之设。固是常事。然当有而不有。此尤其德之盛也。 殿下清心省欲。不置嫔侍。此 殿下圣德最高处也。今因诸臣之言。忽有此 教。此亦恐为怒所动也。若 圣意诚谓言根当覈。则何不于谏院及李命俊等疏劄之入。即 命覈出。诚欲置嫔侍。则何不于此事未发之前有此 教乎。今此举措。窃恐其有乖于圣人喜怒之正。而臣民有以窥 殿下之浅深也。 殿下既恶备局之言不出于平心。而 殿下之举措。亦不能出于平心。如是则其不亦近于尤而效之乎。且大臣。国之柱石。 殿下平日。敬之至矣。今以一言之过。深斥而痛折之。不少假借如此。大臣其何能自安于心乎。君臣之间。情意不交如是。而能成功业者。未之有也。虽在治平之日。尚忧无邦之戒。况当此艰虞之时。只因辞语之过。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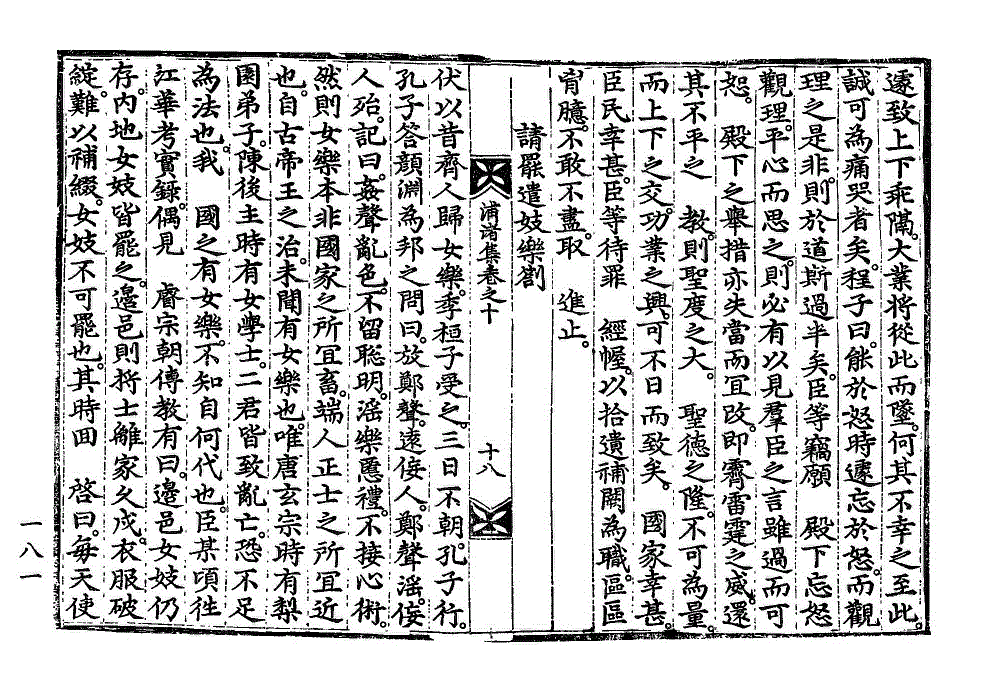 遽致上下乖隔。大业将从此而坠。何其不幸之至此。诚可为痛哭者矣。程子曰。能于怒时遽忘于怒。而观理之是非。则于道斯过半矣。臣等窃愿 殿下忘怒观理。平心而思之。则必有以见群臣之言虽过而可恕。 殿下之举措亦失当而宜改。即霁雷霆之威。还其不平之 教。则圣度之大。 圣德之隆。不可为量。而上下之交。功业之兴。可不日而致矣。 国家幸甚。臣民幸甚。臣等待罪 经幄。以拾遗补阙为职。区区胸臆。不敢不尽。取 进止。
遽致上下乖隔。大业将从此而坠。何其不幸之至此。诚可为痛哭者矣。程子曰。能于怒时遽忘于怒。而观理之是非。则于道斯过半矣。臣等窃愿 殿下忘怒观理。平心而思之。则必有以见群臣之言虽过而可恕。 殿下之举措亦失当而宜改。即霁雷霆之威。还其不平之 教。则圣度之大。 圣德之隆。不可为量。而上下之交。功业之兴。可不日而致矣。 国家幸甚。臣民幸甚。臣等待罪 经幄。以拾遗补阙为职。区区胸臆。不敢不尽。取 进止。请罢遣妓乐劄
伏以昔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孔子答颜渊为邦之问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记曰。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然则女乐本非国家之所宜畜。端人正士之所宜近也。自古帝王之治。未闻有女乐也。唯唐玄宗时有梨园弟子。陈后主时有女学士。二君皆致乱亡。恐不足为法也。我 国之有女乐。不知自何代也。臣某顷往江华考实录。偶见 睿宗朝传教有曰。边邑女妓仍存。内地女妓皆罢之。边邑则将士离家久戍。衣服破绽。难以补缀。女妓不可罢也。其时回 启曰。每天使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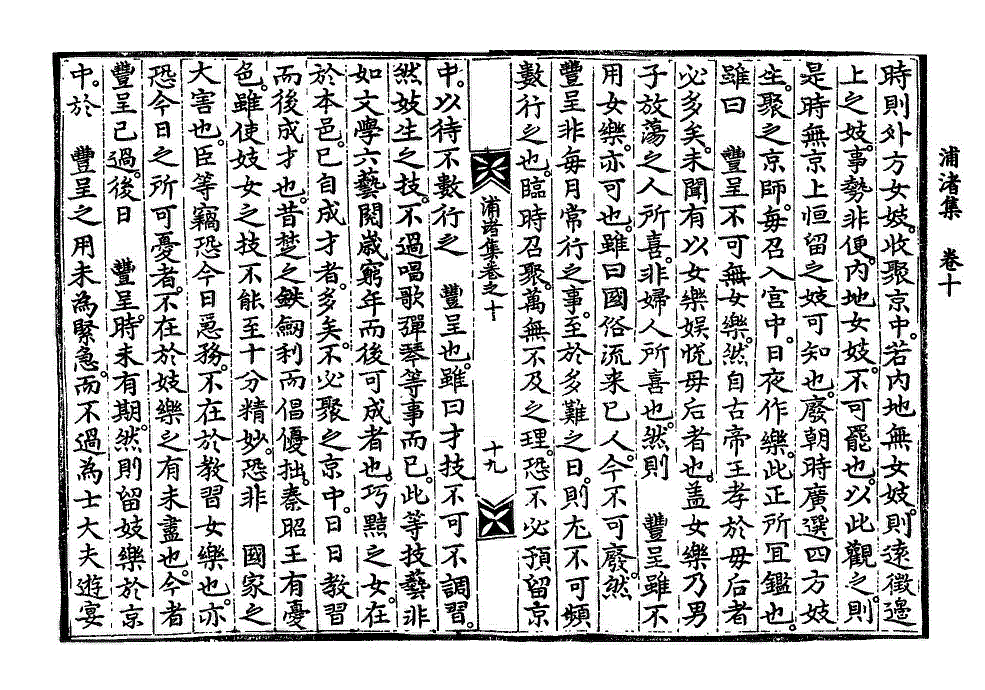 时则外方女妓。收聚京中。若内地无女妓。则远徵边上之妓。事势非便。内地女妓。不可罢也。以此观之。则是时无京上恒留之妓可知也。废朝时广选四方妓生。聚之京师。每召入宫中。日夜作乐。此正所宜鉴也。虽曰 丰呈不可无女乐。然自古帝王孝于母后者必多矣。未闻有以女乐娱悦母后者也。盖女乐乃男子于荡之人所喜。非妇人所喜也。然则 丰呈虽不用女乐。亦可也。虽曰国俗流来已久。今不可废。然 丰呈非每月常行之事。至于多难之日。则尤不可频数行之也。临时召聚。万无不及之理。恐不必预留京中。以待不数行之 丰呈也。虽曰才技不可不调习。然妓生之技。不过唱歌弹琴等事而已。此等技艺非如文学六艺阅岁穷年而后可成者也。巧黠之女。在于本邑。已自成才者。多矣。不必聚之京中。日日教习而后成才也。昔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秦昭王有忧色。虽使妓女之技不能至十分精妙。恐非 国家之大害也。臣等窃恐今日急务。不在于教习女乐也。亦恐今日之所可忧者。不在于妓乐之有未尽也。今者丰呈已过。后日 丰呈。时未有期。然则留妓乐于京中。于 丰呈之用未为紧急。而不过为士大夫游宴
时则外方女妓。收聚京中。若内地无女妓。则远徵边上之妓。事势非便。内地女妓。不可罢也。以此观之。则是时无京上恒留之妓可知也。废朝时广选四方妓生。聚之京师。每召入宫中。日夜作乐。此正所宜鉴也。虽曰 丰呈不可无女乐。然自古帝王孝于母后者必多矣。未闻有以女乐娱悦母后者也。盖女乐乃男子于荡之人所喜。非妇人所喜也。然则 丰呈虽不用女乐。亦可也。虽曰国俗流来已久。今不可废。然 丰呈非每月常行之事。至于多难之日。则尤不可频数行之也。临时召聚。万无不及之理。恐不必预留京中。以待不数行之 丰呈也。虽曰才技不可不调习。然妓生之技。不过唱歌弹琴等事而已。此等技艺非如文学六艺阅岁穷年而后可成者也。巧黠之女。在于本邑。已自成才者。多矣。不必聚之京中。日日教习而后成才也。昔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秦昭王有忧色。虽使妓女之技不能至十分精妙。恐非 国家之大害也。臣等窃恐今日急务。不在于教习女乐也。亦恐今日之所可忧者。不在于妓乐之有未尽也。今者丰呈已过。后日 丰呈。时未有期。然则留妓乐于京中。于 丰呈之用未为紧急。而不过为士大夫游宴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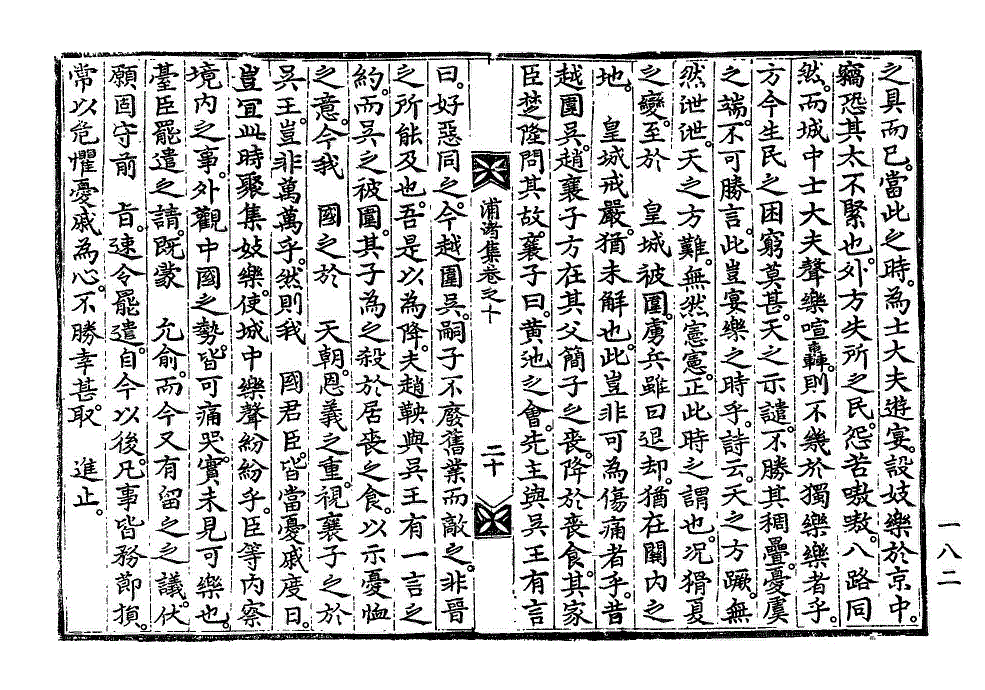 之具而已。当此之时。为士大夫游宴。设妓乐于京中。窃恐其太不紧也。外方失所之民。怨苦嗷嗷。八路同然。而城中士大夫声乐喧轰。则不几于独乐乐者乎。方今生民之困穷莫甚。天之示谴。不胜其稠叠。忧虞之端。不可胜言。此岂宴乐之时乎。诗云。天之方蹶。无然泄泄。天之方难。无然宪宪。正此时之谓也。况猾夏之变。至于 皇城被围。虏兵虽曰退却。犹在关内之地。 皇城戒严。犹未解也。此岂非可为伤痛者乎。昔越围吴。赵襄子方在其父简子之丧。降于丧食。其家臣楚隆问其故。襄子曰。黄池之会。先主与吴王有言曰。好恶同之。今越围吴。嗣子不废旧业而敌之。非晋之所能及也。吾是以为降。夫赵鞅与吴王有一言之约。而吴之被围。其子为之杀于居丧之食。以示忧恤之意。今我 国之于 天朝。恩义之重。视襄子之于吴王。岂非万万乎。然则我 国君臣。皆当忧戚度日。岂宜此时聚集妓乐。使城中乐声纷纷乎。臣等内察境内之事。外观中国之势。皆可痛哭。实未见可乐也。台臣罢遣之请。既蒙 允俞。而今又有留之之议。伏愿固守前 旨。速令罢遣。自今以后。凡事皆务节损。常以危惧忧戚为心。不胜幸甚。取 进止。
之具而已。当此之时。为士大夫游宴。设妓乐于京中。窃恐其太不紧也。外方失所之民。怨苦嗷嗷。八路同然。而城中士大夫声乐喧轰。则不几于独乐乐者乎。方今生民之困穷莫甚。天之示谴。不胜其稠叠。忧虞之端。不可胜言。此岂宴乐之时乎。诗云。天之方蹶。无然泄泄。天之方难。无然宪宪。正此时之谓也。况猾夏之变。至于 皇城被围。虏兵虽曰退却。犹在关内之地。 皇城戒严。犹未解也。此岂非可为伤痛者乎。昔越围吴。赵襄子方在其父简子之丧。降于丧食。其家臣楚隆问其故。襄子曰。黄池之会。先主与吴王有言曰。好恶同之。今越围吴。嗣子不废旧业而敌之。非晋之所能及也。吾是以为降。夫赵鞅与吴王有一言之约。而吴之被围。其子为之杀于居丧之食。以示忧恤之意。今我 国之于 天朝。恩义之重。视襄子之于吴王。岂非万万乎。然则我 国君臣。皆当忧戚度日。岂宜此时聚集妓乐。使城中乐声纷纷乎。臣等内察境内之事。外观中国之势。皆可痛哭。实未见可乐也。台臣罢遣之请。既蒙 允俞。而今又有留之之议。伏愿固守前 旨。速令罢遣。自今以后。凡事皆务节损。常以危惧忧戚为心。不胜幸甚。取 进止。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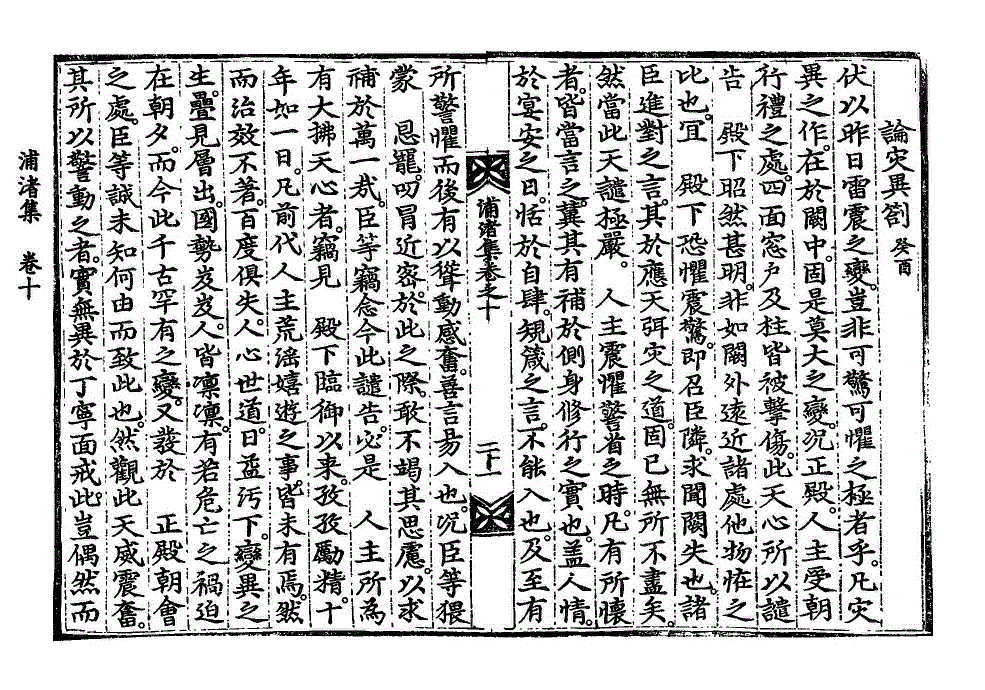 论灾异劄(癸酉)
论灾异劄(癸酉)伏以昨日雷震之变。岂非可惊可惧之极者乎。凡灾异之作。在于阙中。固是莫大之变。况正殿。人主受朝行礼之处。四面窗户及柱皆被击伤。此天心所以谴告 殿下昭然甚明。非如阙外远近诸处他物怪之比也。宜 殿下恐惧震惊。即召臣邻。求闻阙失也。诸臣进对之言。其于应天弭灾之道。固已无所不尽矣。然当此天谴极严。 人主震惧警省之时。凡有所怀者。皆当言之。冀其有补于侧身修行之实也。盖人情。于宴安之日。恬于自肆。规箴之言。不能入也。及至有所警惧而后有以耸动感奋。善言易入也。况臣等猥蒙 恩宠。叨冒近密。于此之际。敢不竭其思虑。以求补于万一哉。臣等窃念今此谴告。必是 人主所为有大拂天心者。窃见 殿下临御以来。孜孜励精。十年如一日。凡前代人主荒淫嬉游之事。皆未有焉。然而治效不著。百度俱失。人心世道。日益污下。变异之生。叠见层出。国势岌岌。人皆凛凛。有若危亡之祸迫在朝夕。而今此千古罕有之变。又发于 正殿朝会之处。臣等诚未知何由而致此也。然观此天威震奋。其所以警动之者。实无异于丁宁面戒。此岂偶然而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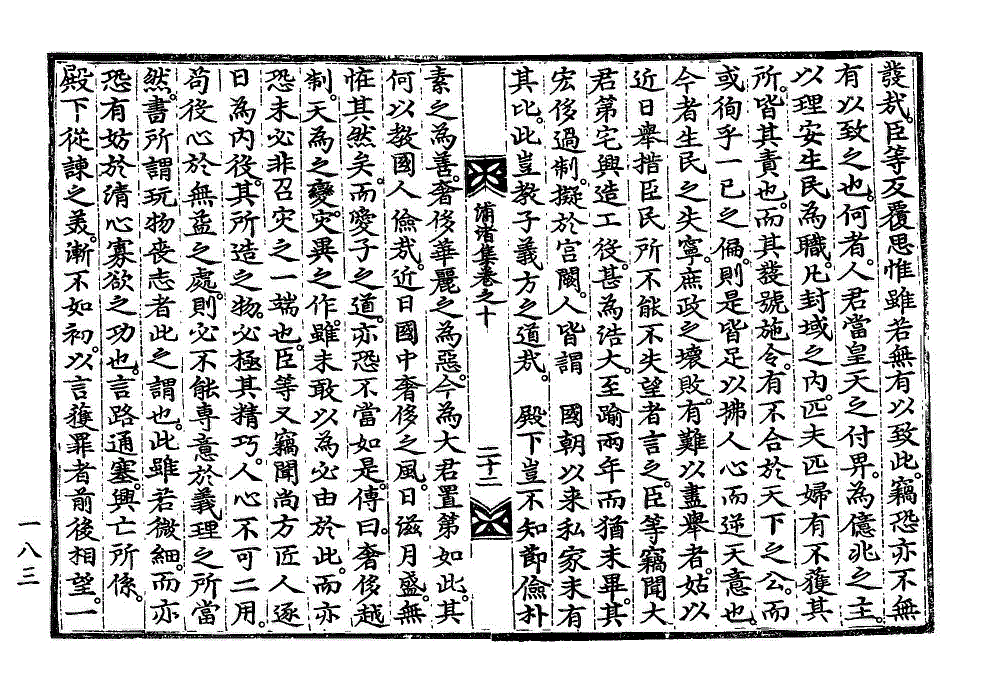 发哉。臣等反覆思惟虽若无有以致此。窃恐亦不无有以致之也。何者。人君当皇天之付畀。为亿兆之主。以理安生民为职。凡封域之内。匹夫匹妇有不获其所。皆其责也。而其发号施令。有不合于天下之公。而或徇乎一己之偏。则是皆足以拂人心而逆天意也。今者生民之失宁。庶政之坏败。有难以尽举者。姑以近日举措臣民所不能不失望者言之。臣等窃闻大君第宅兴造工役。甚为浩大。至踰两年而犹未毕。其宏侈过制。拟于宫阙。人皆谓 国朝以来私家未有其比。此岂教子义方之道哉。 殿下岂不知节俭朴素之为善。奢侈华丽之为恶。今为大君置第如此。其何以教国人俭哉。近日国中奢侈之风。日滋月盛。无怪其然矣。而爱子之道。亦恐不当如是。传曰。奢侈越制。天为之变。灾异之作。虽未敢以为必由于此。而亦恐未必非召灾之一端也。臣等又窃闻尚方匠人逐日为内役。其所造之物。必极其精巧。人心不可二用。苟役心于无益之处。则必不能专意于义理之所当然。书所谓玩物丧志者此之谓也。此虽若微细。而亦恐有妨于清心寡欲之功也。言路通塞。兴亡所系。 殿下从谏之美。渐不如初。以言获罪者前后相望。一
发哉。臣等反覆思惟虽若无有以致此。窃恐亦不无有以致之也。何者。人君当皇天之付畀。为亿兆之主。以理安生民为职。凡封域之内。匹夫匹妇有不获其所。皆其责也。而其发号施令。有不合于天下之公。而或徇乎一己之偏。则是皆足以拂人心而逆天意也。今者生民之失宁。庶政之坏败。有难以尽举者。姑以近日举措臣民所不能不失望者言之。臣等窃闻大君第宅兴造工役。甚为浩大。至踰两年而犹未毕。其宏侈过制。拟于宫阙。人皆谓 国朝以来私家未有其比。此岂教子义方之道哉。 殿下岂不知节俭朴素之为善。奢侈华丽之为恶。今为大君置第如此。其何以教国人俭哉。近日国中奢侈之风。日滋月盛。无怪其然矣。而爱子之道。亦恐不当如是。传曰。奢侈越制。天为之变。灾异之作。虽未敢以为必由于此。而亦恐未必非召灾之一端也。臣等又窃闻尚方匠人逐日为内役。其所造之物。必极其精巧。人心不可二用。苟役心于无益之处。则必不能专意于义理之所当然。书所谓玩物丧志者此之谓也。此虽若微细。而亦恐有妨于清心寡欲之功也。言路通塞。兴亡所系。 殿下从谏之美。渐不如初。以言获罪者前后相望。一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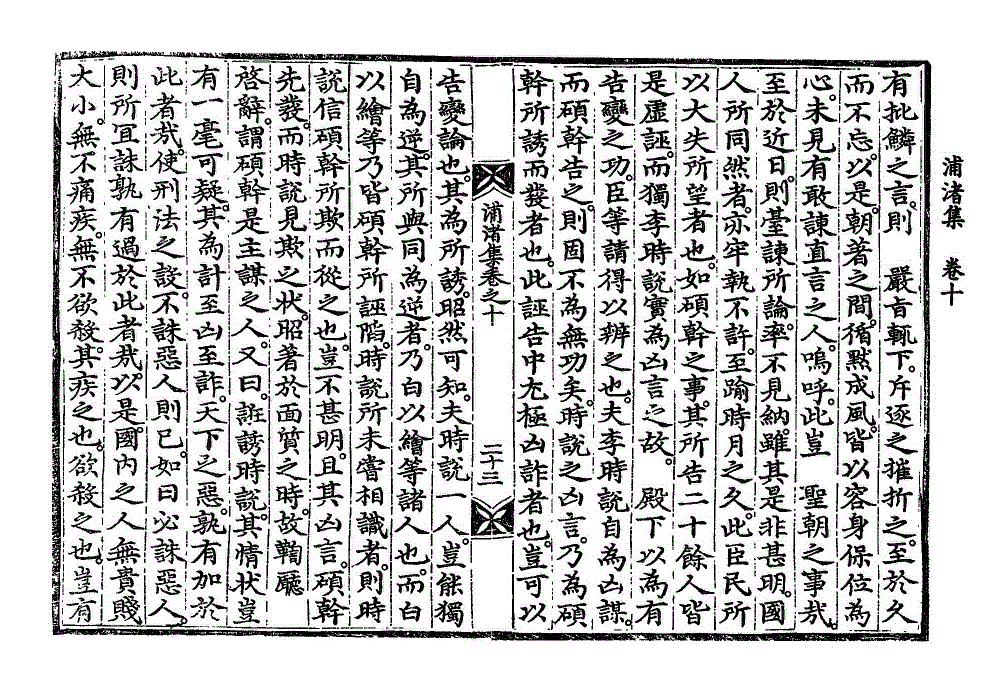 有批鳞之言。则 严旨辄下。斥逐之摧折之。至于久而不忘。以是。朝著之间。循默成风。皆以容身保位为心。未见有敢谏直言之人。呜呼。此岂 圣朝之事哉。至于近日。则台谏所论。率不见纳。虽其是非甚明。国人所同然者。亦牢执不许。至踰时月之久。此臣民所以大失所望者也。如硕干之事。其所告二十馀人皆是虚诬。而独李时说实为凶言之故。 殿下以为有告变之功。臣等请得以辨之也。夫李时说自为凶谋。而硕干告之。则固不为无功矣。时说之凶言。乃为硕干所诱而发者也。此诬告中尤极凶诈者也。岂可以告变论也。其为所诱。昭然可知。夫时说一人。岂能独自为逆。其所与同为逆者。乃白以绘等诸人也。而白以绘等乃皆硕干所诬陷。时说所未尝相识者。则时说信硕干所欺而从之也。岂不甚明。且其凶言。硕干先发。而时说见欺之状。昭著于面质之时。故鞫厅 启辞。谓硕干是主谋之人。又曰。诳诱时说。其情状岂有一毫可疑。其为计至凶至诈。天下之恶。孰有加于此者哉。使刑法之设。不诛恶人则已。如曰必诛恶人。则所宜诛孰有过于此者哉。以是。国内之人无贵贱大小。无不痛疾。无不欲杀。其疾之也。欲杀之也。岂有
有批鳞之言。则 严旨辄下。斥逐之摧折之。至于久而不忘。以是。朝著之间。循默成风。皆以容身保位为心。未见有敢谏直言之人。呜呼。此岂 圣朝之事哉。至于近日。则台谏所论。率不见纳。虽其是非甚明。国人所同然者。亦牢执不许。至踰时月之久。此臣民所以大失所望者也。如硕干之事。其所告二十馀人皆是虚诬。而独李时说实为凶言之故。 殿下以为有告变之功。臣等请得以辨之也。夫李时说自为凶谋。而硕干告之。则固不为无功矣。时说之凶言。乃为硕干所诱而发者也。此诬告中尤极凶诈者也。岂可以告变论也。其为所诱。昭然可知。夫时说一人。岂能独自为逆。其所与同为逆者。乃白以绘等诸人也。而白以绘等乃皆硕干所诬陷。时说所未尝相识者。则时说信硕干所欺而从之也。岂不甚明。且其凶言。硕干先发。而时说见欺之状。昭著于面质之时。故鞫厅 启辞。谓硕干是主谋之人。又曰。诳诱时说。其情状岂有一毫可疑。其为计至凶至诈。天下之恶。孰有加于此者哉。使刑法之设。不诛恶人则已。如曰必诛恶人。则所宜诛孰有过于此者哉。以是。国内之人无贵贱大小。无不痛疾。无不欲杀。其疾之也。欲杀之也。岂有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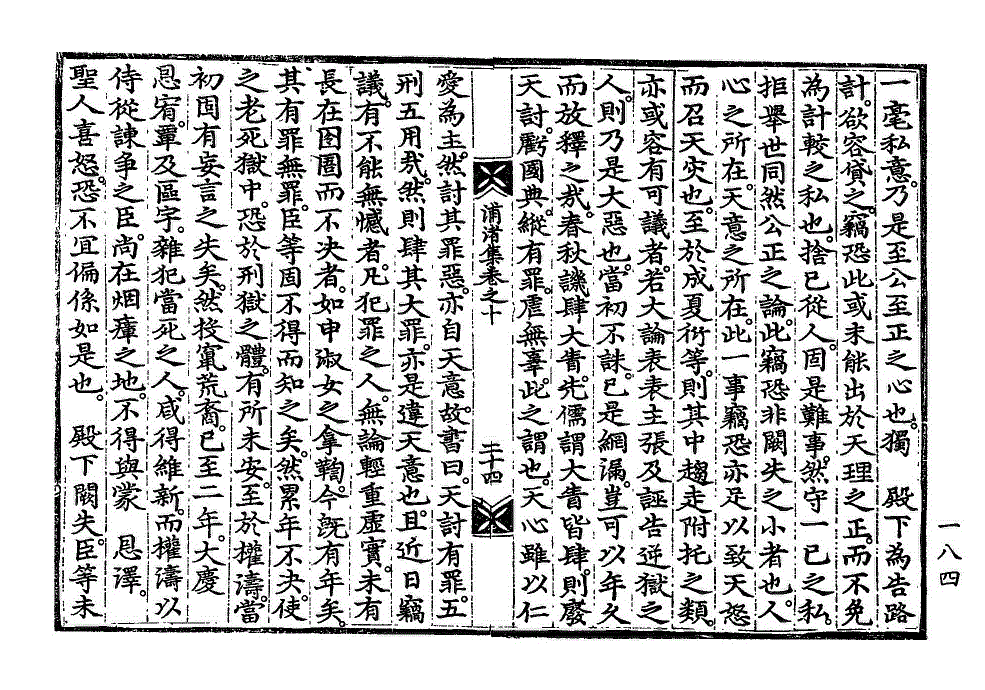 一毫私意。乃是至公至正之心也。独 殿下为告路计。欲容贷之。窃恐此或未能出于天理之正。而不免为计较之私也。舍己从人。固是难事。然守一己之私。拒举世同然公正之论。此窃恐非阙失之小者也。人心之所在。天意之所在。此一事窃恐亦足以致天怒而召天灾也。至于成夏衍等。则其中趋走附托之类。亦或容有可议者。若大论表表主张及诬告逆狱之人。则乃是大恶也。当初不诛。已是网漏。岂可以年久而放释之哉。春秋讥肆大眚。先儒谓大眚皆肆。则废天讨。亏国典。纵有罪。虐无辜。此之谓也。天心虽以仁爱为主。然讨其罪恶。亦自天意。故书曰。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然则肆其大罪。亦是违天意也。且近日窃议。有不能无憾者。凡犯罪之人。无论轻重虚实。未有长在囹圄而不决者。如申淑女之拿鞫。今既有年矣。其有罪无罪。臣等固不得而知之矣。然累年不决。使之老死狱中。恐于刑狱之体。有所未安。至于权涛。当初固有妄言之失矣。然投窜荒裔。已至二年。大庆 恩宥。覃及区宇。杂犯当死之人。咸得维新。而权涛以侍从谏争之臣。尚在烟瘴之地。不得与蒙 恩泽。 圣人喜怒。恐不宜偏系如是也。 殿下阙失。臣等未
一毫私意。乃是至公至正之心也。独 殿下为告路计。欲容贷之。窃恐此或未能出于天理之正。而不免为计较之私也。舍己从人。固是难事。然守一己之私。拒举世同然公正之论。此窃恐非阙失之小者也。人心之所在。天意之所在。此一事窃恐亦足以致天怒而召天灾也。至于成夏衍等。则其中趋走附托之类。亦或容有可议者。若大论表表主张及诬告逆狱之人。则乃是大恶也。当初不诛。已是网漏。岂可以年久而放释之哉。春秋讥肆大眚。先儒谓大眚皆肆。则废天讨。亏国典。纵有罪。虐无辜。此之谓也。天心虽以仁爱为主。然讨其罪恶。亦自天意。故书曰。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然则肆其大罪。亦是违天意也。且近日窃议。有不能无憾者。凡犯罪之人。无论轻重虚实。未有长在囹圄而不决者。如申淑女之拿鞫。今既有年矣。其有罪无罪。臣等固不得而知之矣。然累年不决。使之老死狱中。恐于刑狱之体。有所未安。至于权涛。当初固有妄言之失矣。然投窜荒裔。已至二年。大庆 恩宥。覃及区宇。杂犯当死之人。咸得维新。而权涛以侍从谏争之臣。尚在烟瘴之地。不得与蒙 恩泽。 圣人喜怒。恐不宜偏系如是也。 殿下阙失。臣等未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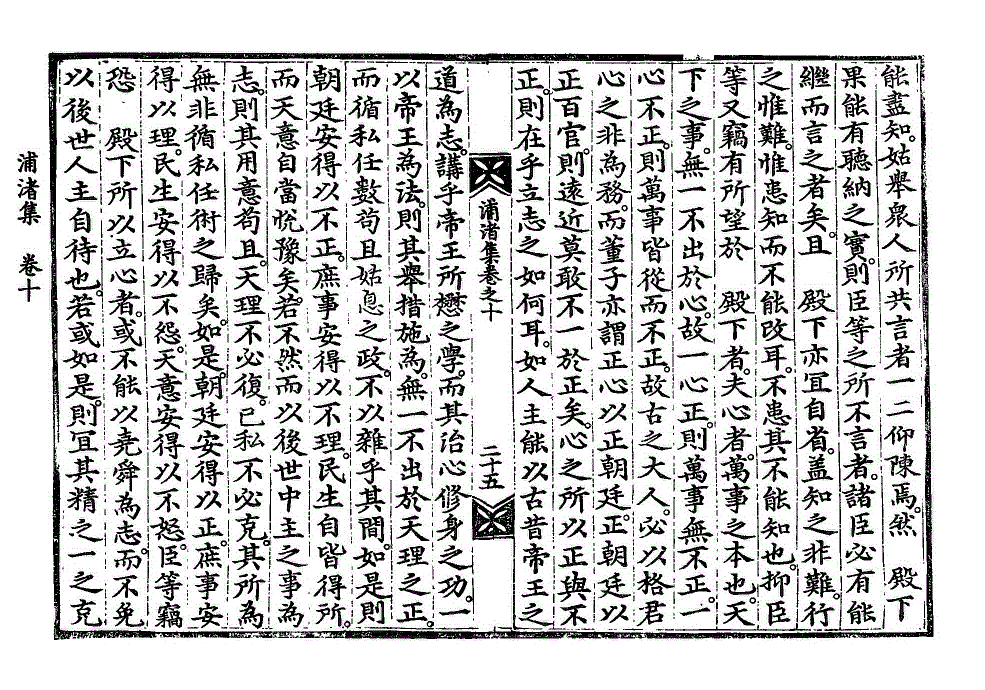 能尽知。姑举众人所共言者一二仰陈焉。然 殿下果能有听纳之实。则臣等之所不言者。诸臣必有能继而言之者矣。且 殿下亦宜自省。盖知之非难。行之惟难。惟患知而不能改耳。不患其不能知也。抑臣等又窃有所望于 殿下者。夫心者。万事之本也。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心。故一心正。则万事无不正。一心不正。则万事皆从而不正。故古之大人。必以格君心之非为务。而董子亦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则远近莫敢不一于正矣。心之所以正与不正。则在乎立志之如何耳。如人主能以古昔帝王之道为志。讲乎帝王所懋之学。而其治心修身之功。一以帝王为法。则其举措施为。无一不出于天理之正。而循私任数苟且姑息之政。不以杂乎其间。如是则朝廷安得以不正。庶事安得以不理。民生自皆得所。而天意自当悦豫矣。若不然而以后世中主之事为志。则其用意苟且。天理不必复。己私不必克。其所为无非循私任术之归矣。如是。朝廷安得以正。庶事安得以理。民生安得以不怨。天意安得以不怒。臣等窃恐 殿下所以立心者。或不能以尧舜为志。而不免以后世人主自待也。若或如是。则宜其精之一之克
能尽知。姑举众人所共言者一二仰陈焉。然 殿下果能有听纳之实。则臣等之所不言者。诸臣必有能继而言之者矣。且 殿下亦宜自省。盖知之非难。行之惟难。惟患知而不能改耳。不患其不能知也。抑臣等又窃有所望于 殿下者。夫心者。万事之本也。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心。故一心正。则万事无不正。一心不正。则万事皆从而不正。故古之大人。必以格君心之非为务。而董子亦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则远近莫敢不一于正矣。心之所以正与不正。则在乎立志之如何耳。如人主能以古昔帝王之道为志。讲乎帝王所懋之学。而其治心修身之功。一以帝王为法。则其举措施为。无一不出于天理之正。而循私任数苟且姑息之政。不以杂乎其间。如是则朝廷安得以不正。庶事安得以不理。民生自皆得所。而天意自当悦豫矣。若不然而以后世中主之事为志。则其用意苟且。天理不必复。己私不必克。其所为无非循私任术之归矣。如是。朝廷安得以正。庶事安得以理。民生安得以不怨。天意安得以不怒。臣等窃恐 殿下所以立心者。或不能以尧舜为志。而不免以后世人主自待也。若或如是。则宜其精之一之克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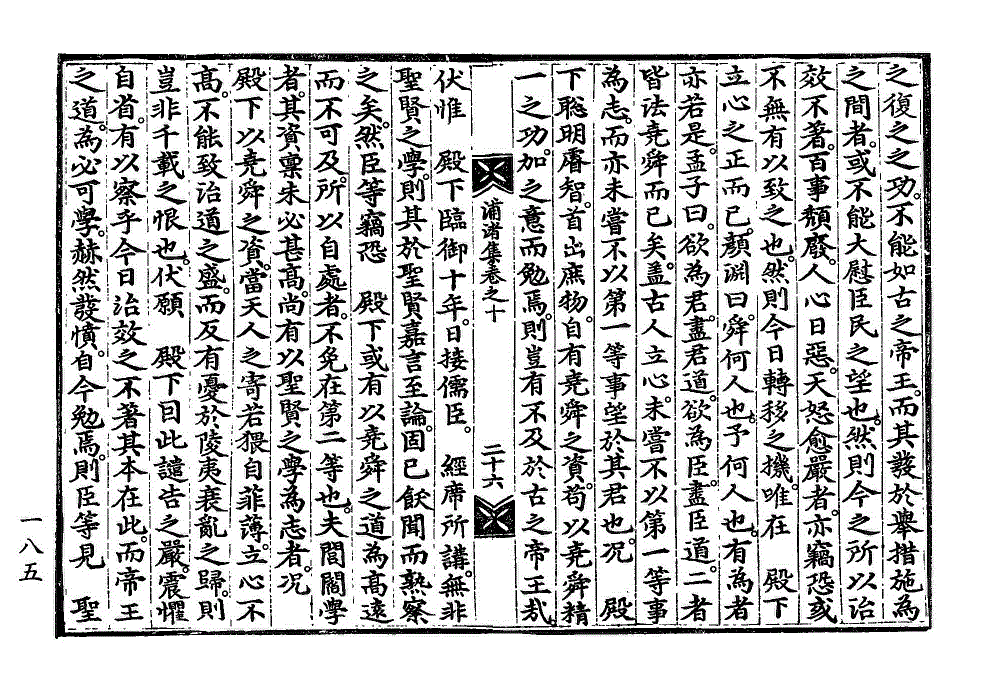 之复之之功。不能如古之帝王。而其发于举措施为之间者。或不能大慰臣民之望也。然则今之所以治效不著。百事颓废。人心日恶。天怒愈严者。亦窃恐或不无有以致之也。然则今日转移之机。唯在 殿下立心之正而已。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曰。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盖古人立心。未尝不以第一等事为志。而亦未尝不以第一等事望于其君也。况 殿下聪明睿智。首出庶物。自有尧舜之资。苟以尧舜精一之功。加之意而勉焉。则岂有不及于古之帝王哉。伏惟 殿下临御十年。日接儒臣。 经席所讲。无非圣贤之学。则其于圣贤嘉言至论。固已饫闻而熟察之矣。然臣等窃恐 殿下或有以尧舜之道为高远而不可及。所以自处者。不免在第二等也。夫闾阎学者。其资禀未必甚高。尚有以圣贤之学为志者。况 殿下以尧舜之资。当天人之寄若猥自菲薄。立心不高。不能致治道之盛。而反有忧于陵夷衰乱之归。则岂非千载之恨也。伏愿 殿下因此谴告之严。震惧自省。有以察乎今日治效之不著其本在此。而帝王之道。为必可学。赫然发愤。自今勉焉。则臣等见 圣
之复之之功。不能如古之帝王。而其发于举措施为之间者。或不能大慰臣民之望也。然则今之所以治效不著。百事颓废。人心日恶。天怒愈严者。亦窃恐或不无有以致之也。然则今日转移之机。唯在 殿下立心之正而已。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曰。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盖古人立心。未尝不以第一等事为志。而亦未尝不以第一等事望于其君也。况 殿下聪明睿智。首出庶物。自有尧舜之资。苟以尧舜精一之功。加之意而勉焉。则岂有不及于古之帝王哉。伏惟 殿下临御十年。日接儒臣。 经席所讲。无非圣贤之学。则其于圣贤嘉言至论。固已饫闻而熟察之矣。然臣等窃恐 殿下或有以尧舜之道为高远而不可及。所以自处者。不免在第二等也。夫闾阎学者。其资禀未必甚高。尚有以圣贤之学为志者。况 殿下以尧舜之资。当天人之寄若猥自菲薄。立心不高。不能致治道之盛。而反有忧于陵夷衰乱之归。则岂非千载之恨也。伏愿 殿下因此谴告之严。震惧自省。有以察乎今日治效之不著其本在此。而帝王之道。为必可学。赫然发愤。自今勉焉。则臣等见 圣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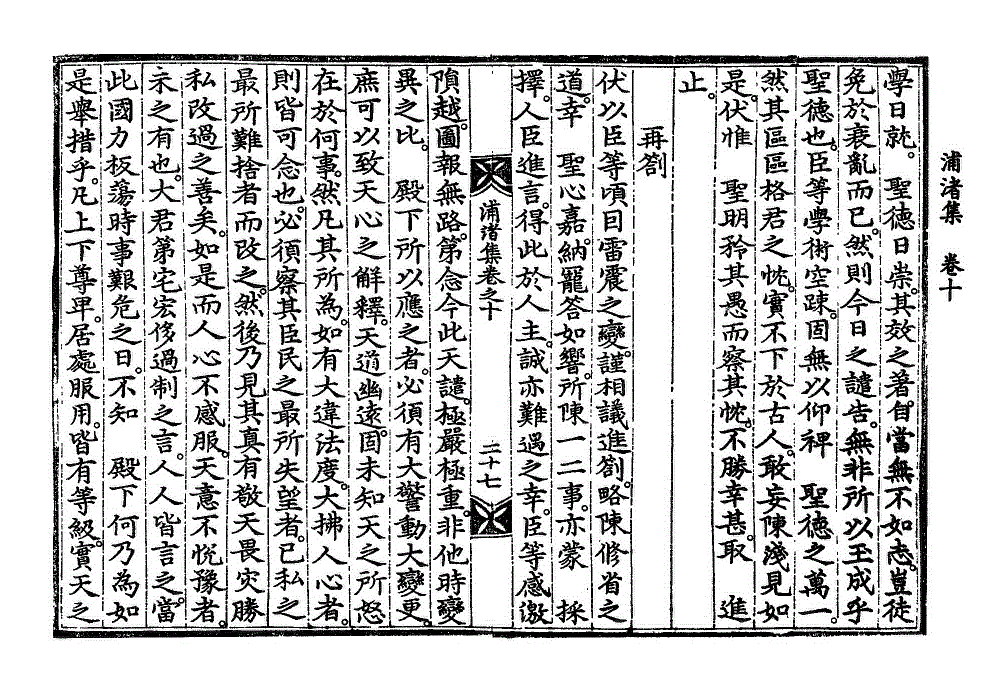 学日就。 圣德日崇。其效之著。自当无不如志。岂徒免于衰乱而已。然则今日之谴告。无非所以玉成乎圣德也。臣等学术空疏。固无以仰裨 圣德之万一。然其区区格君之忱。实不下于古人。敢妄陈浅见如是。伏惟 圣明矜其愚而察其忱。不胜幸甚。取 进止。
学日就。 圣德日崇。其效之著。自当无不如志。岂徒免于衰乱而已。然则今日之谴告。无非所以玉成乎圣德也。臣等学术空疏。固无以仰裨 圣德之万一。然其区区格君之忱。实不下于古人。敢妄陈浅见如是。伏惟 圣明矜其愚而察其忱。不胜幸甚。取 进止。论灾异劄[再劄]
伏以臣等顷因雷震之变。谨相议进劄。略陈修省之道。幸 圣心嘉。纳宠答如响。所陈一二事。亦蒙 采择。人臣进言。得此于人主。诚亦难遇之幸。臣等感激陨越。图报无路。第念今此天谴。极严极重。非他时变异之比。 殿下所以应之者。必须有大警动大变更。庶可以致天心之解释。天道幽远。固未知天之所怒在于何事。然凡其所为。如有大违法度。大拂人心者。则皆可念也。必须察其臣民之最所失望者。己私之最所难舍者而改之。然后乃见其真有敬天畏灾胜私改过之善矣。如是而人心不感服。天意不悦豫者。未之有也。大君第宅宏侈过制之言。人人皆言之。当此国力板荡时事艰危之日。不知 殿下何乃为如是举措乎。凡上下尊卑。居处服用。皆有等级。实天之
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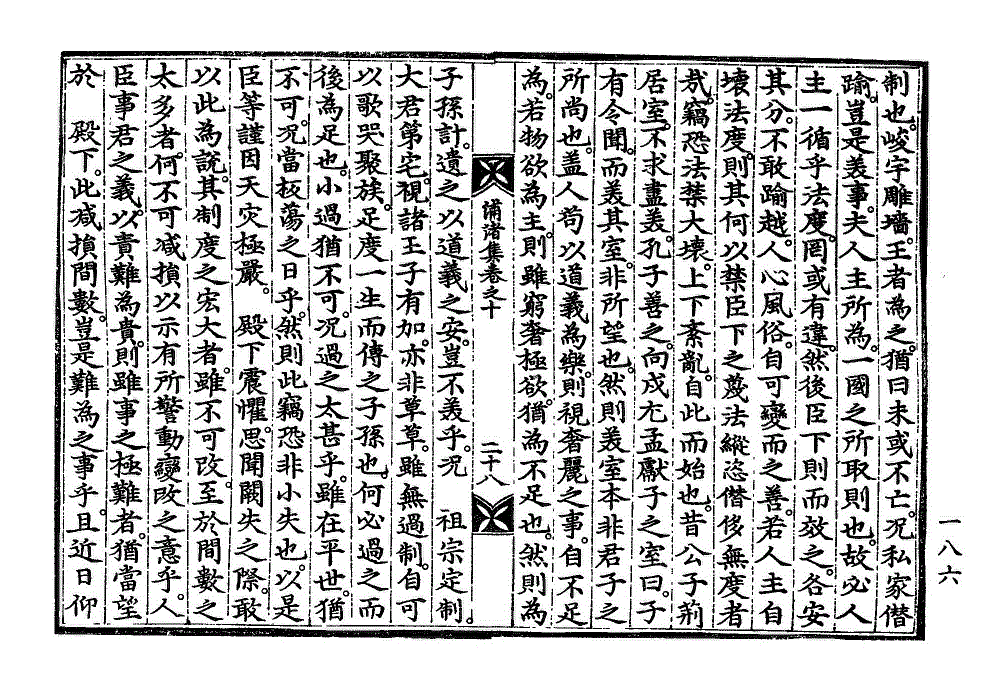 制也。峻宇雕墙。王者为之。犹曰未或不亡。况私家僭踰。岂是美事。夫人主所为。一国之所取则也。故必人主一循乎法度。罔或有违。然后臣下则而效之。各安其分。不敢踰越。人心风俗。自可变而之善。若人主自坏法度。则其何以禁臣下之蔑法纵恣僭侈无度者哉。窃恐法禁大坏。上下紊乱。自此而始也。昔公子荆居室。不求尽美。孔子善之。向戍尤孟献子之室曰。子有令闻。而美其室。非所望也。然则美室本非君子之所尚也。盖人苟以道义为乐。则视奢丽之事。自不足为。若物欲为主。则虽穷奢极欲。犹为不足也。然则为子孙计。遗之以道义之安。岂不美乎。况 祖宗定制。大君第宅。视诸王子有加。亦非草草。虽无过制。自可以歌哭聚族。足度一生而传之子孙也。何必过之而后为足也。小过犹不可。况过之太甚乎。虽在平世。犹不可。况当板荡之日乎。然则此窃恐非小失也。以是臣等谨因天灾极严。 殿下震惧。思闻阙失之际。敢以此为说。其制度之宏大者。虽不可改。至于间数之太多者。何不可减损以示有所警动变改之意乎。人臣事君之义。以责难为贵。则虽事之极难者。犹当望于 殿下。此减损间数。岂是难为之事乎。且近日仰
制也。峻宇雕墙。王者为之。犹曰未或不亡。况私家僭踰。岂是美事。夫人主所为。一国之所取则也。故必人主一循乎法度。罔或有违。然后臣下则而效之。各安其分。不敢踰越。人心风俗。自可变而之善。若人主自坏法度。则其何以禁臣下之蔑法纵恣僭侈无度者哉。窃恐法禁大坏。上下紊乱。自此而始也。昔公子荆居室。不求尽美。孔子善之。向戍尤孟献子之室曰。子有令闻。而美其室。非所望也。然则美室本非君子之所尚也。盖人苟以道义为乐。则视奢丽之事。自不足为。若物欲为主。则虽穷奢极欲。犹为不足也。然则为子孙计。遗之以道义之安。岂不美乎。况 祖宗定制。大君第宅。视诸王子有加。亦非草草。虽无过制。自可以歌哭聚族。足度一生而传之子孙也。何必过之而后为足也。小过犹不可。况过之太甚乎。虽在平世。犹不可。况当板荡之日乎。然则此窃恐非小失也。以是臣等谨因天灾极严。 殿下震惧。思闻阙失之际。敢以此为说。其制度之宏大者。虽不可改。至于间数之太多者。何不可减损以示有所警动变改之意乎。人臣事君之义。以责难为贵。则虽事之极难者。犹当望于 殿下。此减损间数。岂是难为之事乎。且近日仰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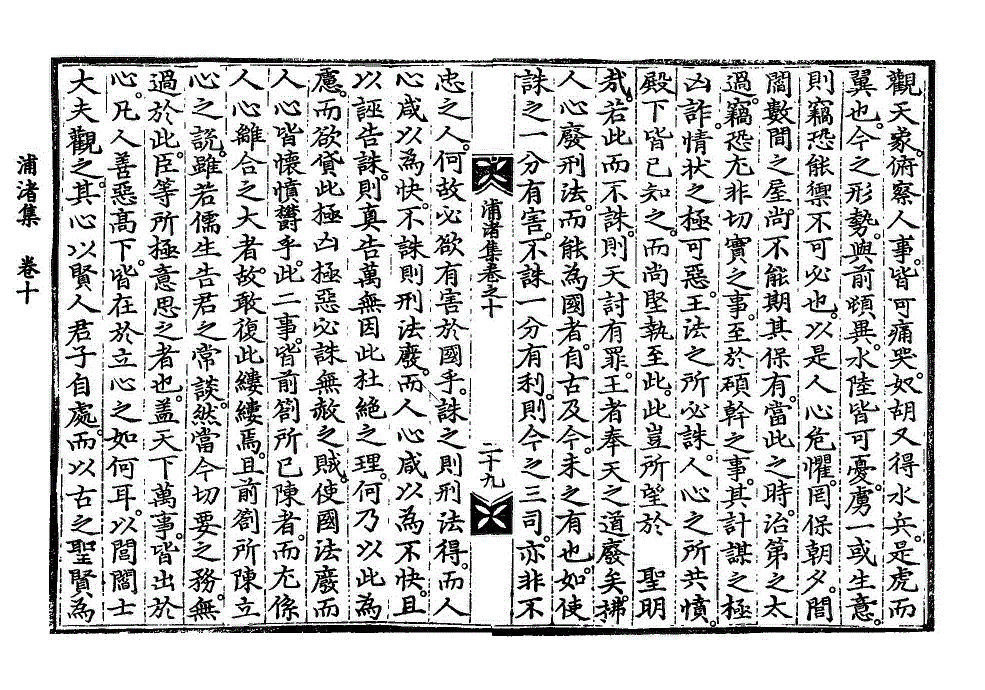 观天象。俯察人事。皆可痛哭。奴胡又得水兵。是虎而翼也。今之形势。与前顿异。水陆皆可忧。虏一或生意。则窃恐能御不可必也。以是人心危惧。罔保朝夕。闾阎数间之屋。尚不能期其保有。当此之时。治第之太过。窃恐尤非切实之事。至于硕干之事。其计谋之极凶诈。情状之极可恶。王法之所必诛。人心之所共愤。殿下皆已知之。而尚坚执至此。此岂所望于 圣明哉。若此而不诛。则天讨有罪。王者奉天之道废矣。拂人心废刑法。而能为国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如使诛之一分有害。不诛一分有利。则今之三司。亦非不忠之人。何故必欲有害于国乎。诛之则刑法得。而人心咸以为快。不诛则刑法废。而人心咸以为不快。且以诬告诛。则真告万无因此杜绝之理。何乃以此为虑。而欲贷此极凶极恶必诛无赦之贼。使国法废而人心皆怀愤郁乎。此二事。皆前劄所已陈者。而尤系人心离合之大者。故敢复此缕缕焉。且前劄所陈立心之说。虽若儒生告君之常谈。然当今切要之务。无过于此。臣等所极意思之者也。盖天下万事。皆出于心。凡人善恶高下。皆在于立心之如何耳。以闾阎士大夫观之。其心以贤人君子自处。而以古之圣贤为
观天象。俯察人事。皆可痛哭。奴胡又得水兵。是虎而翼也。今之形势。与前顿异。水陆皆可忧。虏一或生意。则窃恐能御不可必也。以是人心危惧。罔保朝夕。闾阎数间之屋。尚不能期其保有。当此之时。治第之太过。窃恐尤非切实之事。至于硕干之事。其计谋之极凶诈。情状之极可恶。王法之所必诛。人心之所共愤。殿下皆已知之。而尚坚执至此。此岂所望于 圣明哉。若此而不诛。则天讨有罪。王者奉天之道废矣。拂人心废刑法。而能为国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如使诛之一分有害。不诛一分有利。则今之三司。亦非不忠之人。何故必欲有害于国乎。诛之则刑法得。而人心咸以为快。不诛则刑法废。而人心咸以为不快。且以诬告诛。则真告万无因此杜绝之理。何乃以此为虑。而欲贷此极凶极恶必诛无赦之贼。使国法废而人心皆怀愤郁乎。此二事。皆前劄所已陈者。而尤系人心离合之大者。故敢复此缕缕焉。且前劄所陈立心之说。虽若儒生告君之常谈。然当今切要之务。无过于此。臣等所极意思之者也。盖天下万事。皆出于心。凡人善恶高下。皆在于立心之如何耳。以闾阎士大夫观之。其心以贤人君子自处。而以古之圣贤为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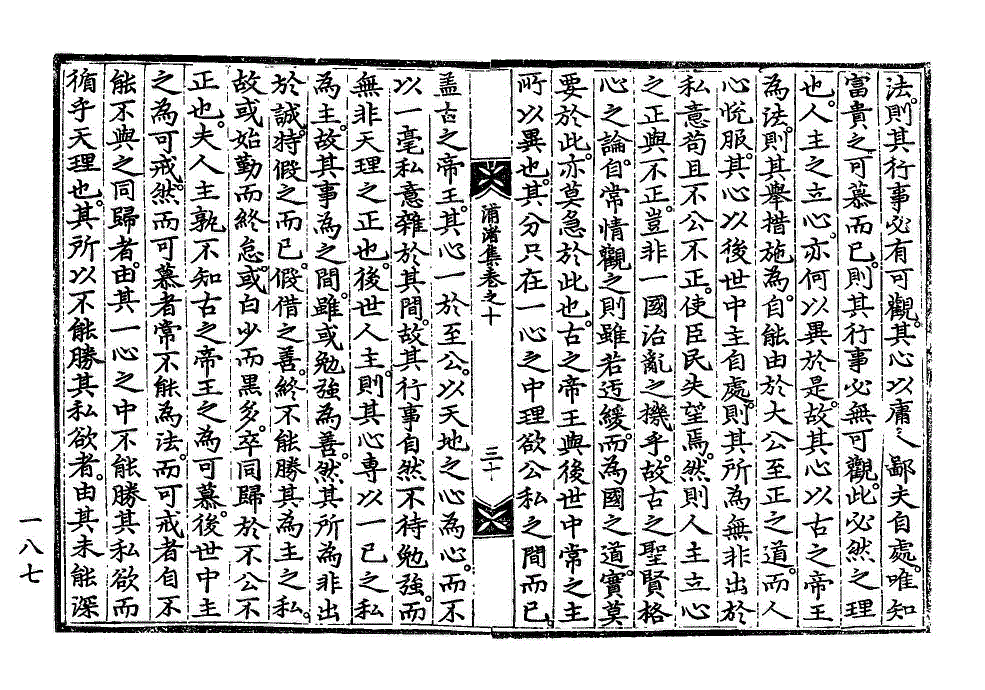 法。则其行事必有可观。其心以庸人鄙夫自处。唯知富贵之可慕而已。则其行事必无可观。此必然之理也。人主之立心。亦何以异于是。故其心以古之帝王为法。则其举措施为。自能由于大公至正之道。而人心悦服。其心以后世中主自处。则其所为无非出于私意苟且不公不正。使臣民失望焉。然则人主立心之正与不正。岂非一国治乱之机乎。故古之圣贤格心之论。自常情观之则虽若迂缓。而为国之道。实莫要于此。亦莫急于此也。古之帝王与后世中常之主所以异也。其分只在一心之中理欲公私之间而已。盖古之帝王。其心一于至公。以天地之心为心。而不以一毫私意杂于其间。故其行事自然不待勉强。而无非天理之正也。后世人主。则其心专以一己之私为主。故其事为之间。虽或勉强为善。然其所为非出于诚。特假之而已。假借之善。终不能胜其为主之私。故或始勤而终怠。或白少而黑多。卒同归于不公不正也。夫人主孰不知古之帝王之为可慕。后世中主之为可戒。然而可慕者常不能为法。而可戒者自不能不与之同归者。由其一心之中不能胜其私欲而循乎天理也。其所以不能胜其私欲者。由其未能深
法。则其行事必有可观。其心以庸人鄙夫自处。唯知富贵之可慕而已。则其行事必无可观。此必然之理也。人主之立心。亦何以异于是。故其心以古之帝王为法。则其举措施为。自能由于大公至正之道。而人心悦服。其心以后世中主自处。则其所为无非出于私意苟且不公不正。使臣民失望焉。然则人主立心之正与不正。岂非一国治乱之机乎。故古之圣贤格心之论。自常情观之则虽若迂缓。而为国之道。实莫要于此。亦莫急于此也。古之帝王与后世中常之主所以异也。其分只在一心之中理欲公私之间而已。盖古之帝王。其心一于至公。以天地之心为心。而不以一毫私意杂于其间。故其行事自然不待勉强。而无非天理之正也。后世人主。则其心专以一己之私为主。故其事为之间。虽或勉强为善。然其所为非出于诚。特假之而已。假借之善。终不能胜其为主之私。故或始勤而终怠。或白少而黑多。卒同归于不公不正也。夫人主孰不知古之帝王之为可慕。后世中主之为可戒。然而可慕者常不能为法。而可戒者自不能不与之同归者。由其一心之中不能胜其私欲而循乎天理也。其所以不能胜其私欲者。由其未能深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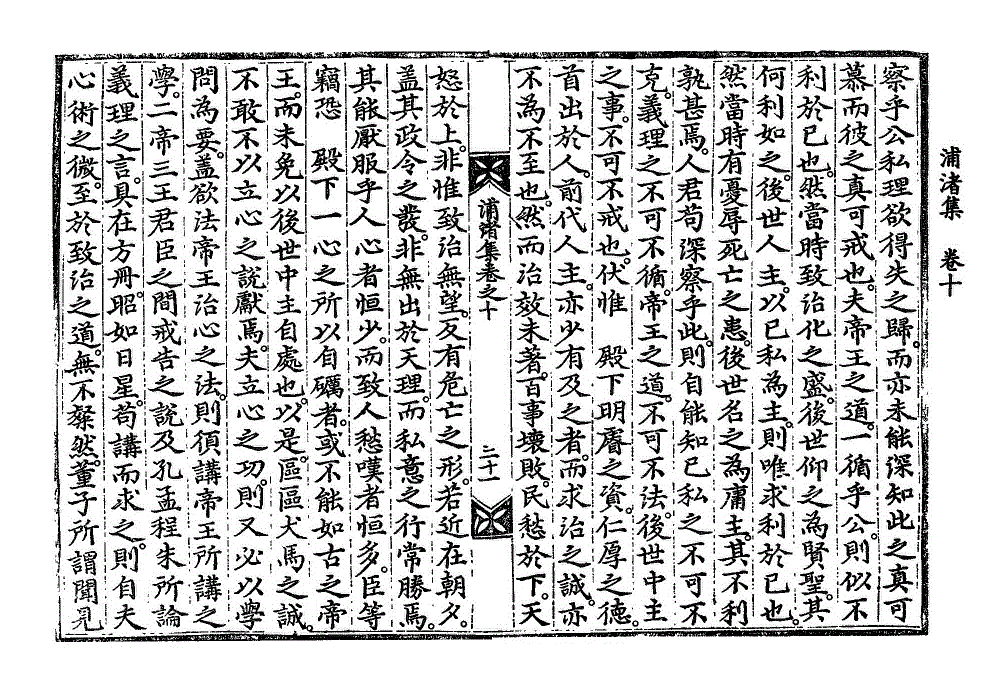 察乎公私理欲得失之归。而亦未能深知此之真可慕而彼之真可戒也。夫帝王之道。一循乎公。则似不利于己也。然当时致治化之盛。后世仰之为贤圣。其何利如之。后世人主。以己私为主。则唯求利于己也。然当时有忧辱死亡之患。后世名之为庸主。其不利孰甚焉。人君苟深察乎此。则自能知己私之不可不克。义理之不可不循。帝王之道。不可不法。后世中主之事。不可不戒也。伏惟 殿下明睿之资。仁厚之德。首出于人。前代人主。亦少有及之者。而求治之诚。亦不为不至也。然而治效未著。百事坏败。民愁于下。天怒于上。非惟致治无望。反有危亡之形。若近在朝夕。盖其政令之发。非无出于天理。而私意之行常胜焉。其能厌服乎人心者恒少。而致人愁叹者恒多。臣等窃恐 殿下一心之所以自砺者。或不能如古之帝王。而未免以后世中主自处也。以是。区区犬马之诚。不敢不以立心之说献焉。夫立心之功。则又必以学问为要。盖欲法帝王治心之法。则须讲帝王所讲之学。二帝三王君臣之间戒告之说及孔孟程朱所论义理之言。具在方册。昭如日星。苟讲而求之。则自夫心术之微。至于致治之道。无不粲然。董子所谓闻见
察乎公私理欲得失之归。而亦未能深知此之真可慕而彼之真可戒也。夫帝王之道。一循乎公。则似不利于己也。然当时致治化之盛。后世仰之为贤圣。其何利如之。后世人主。以己私为主。则唯求利于己也。然当时有忧辱死亡之患。后世名之为庸主。其不利孰甚焉。人君苟深察乎此。则自能知己私之不可不克。义理之不可不循。帝王之道。不可不法。后世中主之事。不可不戒也。伏惟 殿下明睿之资。仁厚之德。首出于人。前代人主。亦少有及之者。而求治之诚。亦不为不至也。然而治效未著。百事坏败。民愁于下。天怒于上。非惟致治无望。反有危亡之形。若近在朝夕。盖其政令之发。非无出于天理。而私意之行常胜焉。其能厌服乎人心者恒少。而致人愁叹者恒多。臣等窃恐 殿下一心之所以自砺者。或不能如古之帝王。而未免以后世中主自处也。以是。区区犬马之诚。不敢不以立心之说献焉。夫立心之功。则又必以学问为要。盖欲法帝王治心之法。则须讲帝王所讲之学。二帝三王君臣之间戒告之说及孔孟程朱所论义理之言。具在方册。昭如日星。苟讲而求之。则自夫心术之微。至于致治之道。无不粲然。董子所谓闻见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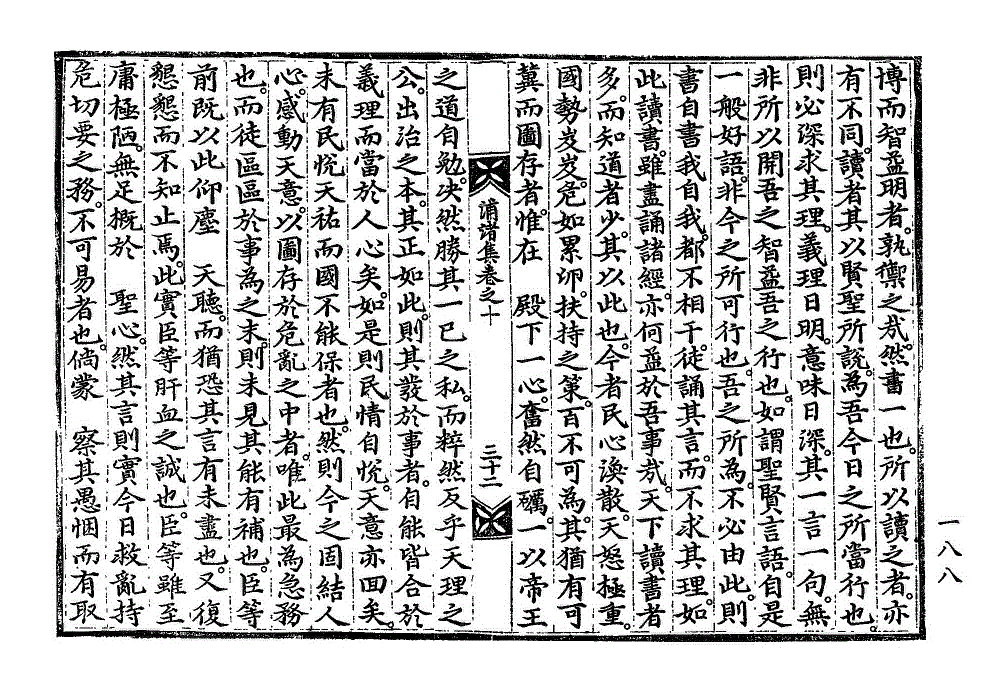 博而智益明者。孰御之哉。然书一也。所以读之者。亦有不同。读者其以贤圣所说。为吾今日之所当行也。则必深求其理。义理日明。意味日深。其一言一句。无非所以开吾之智益吾之行也。如谓圣贤言语。自是一般好语。非今之所可行也。吾之所为。不必由此。则书自书我自我。都不相干。徒诵其言。而不求其理。如此读书。虽尽诵诸经。亦何益于吾事哉。天下读书者多。而知道者少。其以此也。今者民心涣散。天怒极重。国势岌岌。危如累卵。扶持之策。百不可为。其犹有可冀而图存者。惟在 殿下一心。奋然自砺。一以帝王之道自勉。决然胜其一己之私。而粹然反乎天理之公。出治之本。其正如此。则其发于事者。自能皆合于义理而当于人心矣。如是则民情自悦。天意亦回矣。未有民悦天祐而国不能保者也。然则今之固结人心。感动天意。以图存于危乱之中者。唯此最为急务也。而徒区区于事为之末。则未见其能有补也。臣等前既以此仰尘 天听。而犹恐其言有未尽也。又复恳恳而不知止焉。此实臣等肝血之诚也。臣等虽至庸极陋。无足概于 圣心。然其言则实今日救乱持危切要之务。不可易者也。倘蒙 察其愚悃而有取
博而智益明者。孰御之哉。然书一也。所以读之者。亦有不同。读者其以贤圣所说。为吾今日之所当行也。则必深求其理。义理日明。意味日深。其一言一句。无非所以开吾之智益吾之行也。如谓圣贤言语。自是一般好语。非今之所可行也。吾之所为。不必由此。则书自书我自我。都不相干。徒诵其言。而不求其理。如此读书。虽尽诵诸经。亦何益于吾事哉。天下读书者多。而知道者少。其以此也。今者民心涣散。天怒极重。国势岌岌。危如累卵。扶持之策。百不可为。其犹有可冀而图存者。惟在 殿下一心。奋然自砺。一以帝王之道自勉。决然胜其一己之私。而粹然反乎天理之公。出治之本。其正如此。则其发于事者。自能皆合于义理而当于人心矣。如是则民情自悦。天意亦回矣。未有民悦天祐而国不能保者也。然则今之固结人心。感动天意。以图存于危乱之中者。唯此最为急务也。而徒区区于事为之末。则未见其能有补也。臣等前既以此仰尘 天听。而犹恐其言有未尽也。又复恳恳而不知止焉。此实臣等肝血之诚也。臣等虽至庸极陋。无足概于 圣心。然其言则实今日救乱持危切要之务。不可易者也。倘蒙 察其愚悃而有取浦渚先生集卷之十 第 1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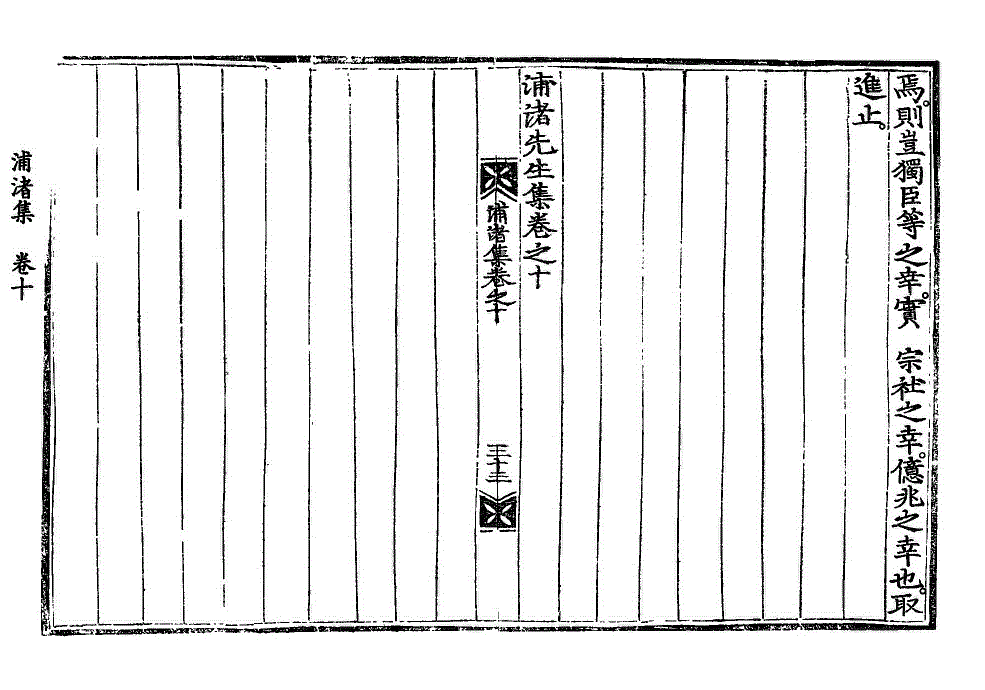 焉。则岂独臣等之幸。实 宗社之幸。亿兆之幸也。取进止。
焉。则岂独臣等之幸。实 宗社之幸。亿兆之幸也。取进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