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x 页
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劄(十四首)
劄(十四首)
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56H 页
 处置两司劄(戊辰)
处置两司劄(戊辰)伏以多官并引嫌而退。许𥡦之告。因洪瑞凤而发。则不可谓之无功。昔汉霍禹等谋反。男子张章先发觉。以语期门董忠。忠告左曹杨恽。恽告侍中金安上。章与忠等皆得封侯。今以许𥡦之书告于朝廷。以是参勋。似无不可。谏院之以为当录。别无错谬之失。至于崔山辉闻秀香之逆谋。告于金澃。使传言于沈命世。实与张章之语董忠无异。不可谓迟告。似无可罪之事。不为论启。亦无不可。人臣闻逆变。不即发告。固为可罪。然上变是何等重事。详审慎密。亦或一道。似不足深罪。洪瑞凤之失。只在论功不均。恐不在发告之迟。不论显然之失。而论其不足深罪之过。且谓不可遽为元勋则可也。至请削勋。似为过激。论事之体。未免失当。前后所闻。自谓差误。则论事失实。在所难免。请大司谏金尚宪等出仕。大司宪郑经世等并 命递差。取 进止。
论 启运宫祔祭主祭之非劄(同日四劄)
伏以 殿下圣孝出天。自巨创之始。号慕之诚。慎终
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56L 页
 之意。无所不用其至。而以宗统之重。不敢径情直行。俯循廷臣之议。于丧服馈奠之节。皆降从追孝本生之礼。既以绫原君辅为丧主。几祭奠皆使主之。而朔望及盛祭。则 殿下必往参焉。以终三年。其追孝之诚。敬宗之义。可谓两尽。可以为法于百世矣。伏见今祔庙仪注。以自 上主祭磨鍊启下。臣等未知祔庙之祭与虞祥等祭有何所异。而独 殿下自主之乎。既有丧主。虞祥等祭。皆全主之。则祔庙独非丧主所当主者乎。 殿下不敢主祭于 魂宫者。以持重于大宗。故不得不降于本生也。今忽自主私庙之祭。其于尊祖敬宗之义。窃恐大有所妨也。且凡礼节。既有一定之制。则不可前后异同。今此磨鍊。实为无据。伏愿 亟从两司之请。使莫重慎终之礼。无所不尽。不胜幸甚。取 进止。
之意。无所不用其至。而以宗统之重。不敢径情直行。俯循廷臣之议。于丧服馈奠之节。皆降从追孝本生之礼。既以绫原君辅为丧主。几祭奠皆使主之。而朔望及盛祭。则 殿下必往参焉。以终三年。其追孝之诚。敬宗之义。可谓两尽。可以为法于百世矣。伏见今祔庙仪注。以自 上主祭磨鍊启下。臣等未知祔庙之祭与虞祥等祭有何所异。而独 殿下自主之乎。既有丧主。虞祥等祭。皆全主之。则祔庙独非丧主所当主者乎。 殿下不敢主祭于 魂宫者。以持重于大宗。故不得不降于本生也。今忽自主私庙之祭。其于尊祖敬宗之义。窃恐大有所妨也。且凡礼节。既有一定之制。则不可前后异同。今此磨鍊。实为无据。伏愿 亟从两司之请。使莫重慎终之礼。无所不尽。不胜幸甚。取 进止。论 启运宫祔祭主祭之非劄[再劄]
伏以祔庙之祭。是丧主应行之祭。若 殿下行之。则是 殿下主其丧也。既有丧主。自初丧虞卒哭及祥禫皆主行之。而至于祔庙。 殿下自主之。未知此何礼也。凡丧礼必有主。故礼曰。丧无无主。既立丧主则他人不得以间之。若 殿下应主此丧。则自初不当
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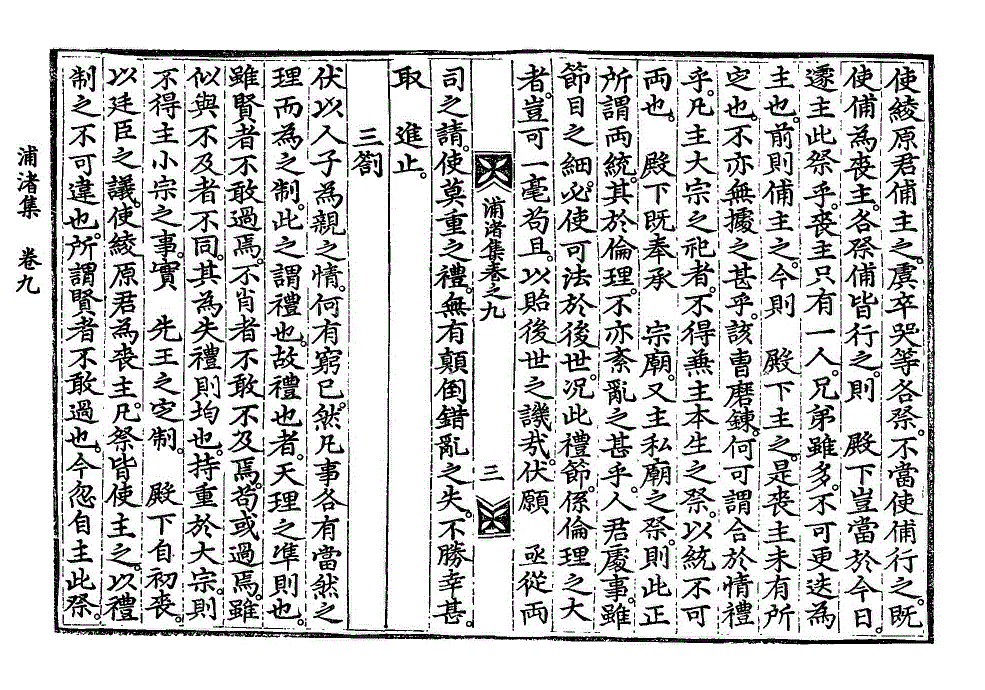 使绫原君辅主之。虞卒哭等各祭。不当使辅行之。既使辅为丧主。各祭辅皆行之。则 殿下岂当于今日。遽主此祭乎。丧主只有一人。兄弟虽多。不可更迭为主也。前则辅主之。今则 殿下主之。是丧主未有所定也。不亦无据之甚乎。该曹磨鍊。何可谓合于情礼乎。凡主大宗之祀者。不得兼主本生之祭。以统不可两也。 殿下既奉承 宗庙。又主私庙之祭。则此正所谓两统。其于伦理。不亦紊乱之甚乎。人君处事。虽节目之细。必使可法于后世。况此礼节。系伦理之大者。岂可一毫苟且。以贻后世之讥哉。伏愿 亟从两司之请。使莫重之礼。无有颠倒错乱之失。不胜幸甚。取 进止。
使绫原君辅主之。虞卒哭等各祭。不当使辅行之。既使辅为丧主。各祭辅皆行之。则 殿下岂当于今日。遽主此祭乎。丧主只有一人。兄弟虽多。不可更迭为主也。前则辅主之。今则 殿下主之。是丧主未有所定也。不亦无据之甚乎。该曹磨鍊。何可谓合于情礼乎。凡主大宗之祀者。不得兼主本生之祭。以统不可两也。 殿下既奉承 宗庙。又主私庙之祭。则此正所谓两统。其于伦理。不亦紊乱之甚乎。人君处事。虽节目之细。必使可法于后世。况此礼节。系伦理之大者。岂可一毫苟且。以贻后世之讥哉。伏愿 亟从两司之请。使莫重之礼。无有颠倒错乱之失。不胜幸甚。取 进止。论 启运宫祔祭主祭之非劄[三劄]
伏以人子为亲之情。何有穷已。然凡事各有当然之理而为之制。此之谓礼也。故礼也者。天理之准则也。虽贤者不敢过焉。不肖者不敢不及焉。苟或过焉。虽似与不及者不同。其为失礼则均也。持重于大宗。则不得主小宗之事。实 先王之定制。 殿下自初丧。以廷臣之议。使绫原君为丧主。凡祭皆使主之。以礼制之不可违也。所谓贤者不敢过也。今忽自主此祭。
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57L 页
 何前后相戾之若此也。以 宗庙言之。则嫌于两统。以私庙言之。则主祀未有所定。于此于彼。无据甚矣。臣等虽无状。忝冒论思。安敢陷 殿下于失礼之归乎。伏愿 亟从两司之请。以正享祀之礼。不胜幸甚。取 进止。
何前后相戾之若此也。以 宗庙言之。则嫌于两统。以私庙言之。则主祀未有所定。于此于彼。无据甚矣。臣等虽无状。忝冒论思。安敢陷 殿下于失礼之归乎。伏愿 亟从两司之请。以正享祀之礼。不胜幸甚。取 进止。论 启运宫祔祭主祭之非劄[四劄]
伏以 殿下自主私庙之祭。非但前后有异。实有妨于宗统。礼之大经乱矣。非如节目间小失也。若 殿下只欲任情。而不必从礼也。则何所不可。如欲以礼从事也。则决不可主此祭也。夫礼者。先王之定制。天理之准则。苟礼义一失则人道坏乱。其弊将至于国非其国也。况帝王行事。为一世之所观仰。尤不可一毫苟且也。孔子以无违告孟孙。人子事亲。苟无违于礼。斯为至矣。不及于礼。固非孝也。过亦违也。其为非孝则均也。夫任情过礼。意本为孝。而反不免为非孝之归。此圣人所以无违为孝也。伏愿深 思礼制之不可违也。 亟从两司之请。不胜幸甚。取 进止。
请还收权涛削黜之 命劄
伏以臣等伏见谏院论乐安郡守林庆业善事之事。举岁馔所送多至二十种为辞。而右议政金瑬。以庆
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58H 页
 业实送臣家。上劄待罪。 殿下至命削黜。发论谏官。夫台谏以言事为职。虽其所论或出于风闻之误。犹不可为罪。况此二十种之说。既非虚妄。此有何罪。臣等窃思岁时馔物之送。自是常事。况庆业出自体府军官之中。则于金瑬。自有情分。异于他宰相。其所送之多。亦人情之常。且所谓二十种者。不过土产饮食等杂物。而或一物而多其名色。非重货之类。此其人只是愚而无识。徒知献忠于主将。务其色名之多为誇耳。在于金瑬。初非有失。庆业之事。察其情则亦不足深罪。然台谏骤闻其一处所送至于二十种之多。未知其曲折。则其骇而恶之。实情性之正也。至于论启。亦职事之所当然也。此岂可为罪也。如使此论之发。一毫有倾陷大臣之意。则 殿下恶而罪之。固宜也。其发论实状。只是如此。此正无情之事也。且故引他事。有意倾陷。乃奸人之事也。今此论出于权涛。涛之为人。决不为此也。大臣以此不安。至于辞位。则 殿下谕而安之可也。至于深罪据事殚(一作弹)劾。出于无情。初非有罪之谏。臣窃恐其于举措。所失不细也。臣等窃见近年来以言事忤 圣旨。不合于朝廷者相继。窃恐 殿下公听。未见直士之有益于 国家也。夫
业实送臣家。上劄待罪。 殿下至命削黜。发论谏官。夫台谏以言事为职。虽其所论或出于风闻之误。犹不可为罪。况此二十种之说。既非虚妄。此有何罪。臣等窃思岁时馔物之送。自是常事。况庆业出自体府军官之中。则于金瑬。自有情分。异于他宰相。其所送之多。亦人情之常。且所谓二十种者。不过土产饮食等杂物。而或一物而多其名色。非重货之类。此其人只是愚而无识。徒知献忠于主将。务其色名之多为誇耳。在于金瑬。初非有失。庆业之事。察其情则亦不足深罪。然台谏骤闻其一处所送至于二十种之多。未知其曲折。则其骇而恶之。实情性之正也。至于论启。亦职事之所当然也。此岂可为罪也。如使此论之发。一毫有倾陷大臣之意。则 殿下恶而罪之。固宜也。其发论实状。只是如此。此正无情之事也。且故引他事。有意倾陷。乃奸人之事也。今此论出于权涛。涛之为人。决不为此也。大臣以此不安。至于辞位。则 殿下谕而安之可也。至于深罪据事殚(一作弹)劾。出于无情。初非有罪之谏。臣窃恐其于举措。所失不细也。臣等窃见近年来以言事忤 圣旨。不合于朝廷者相继。窃恐 殿下公听。未见直士之有益于 国家也。夫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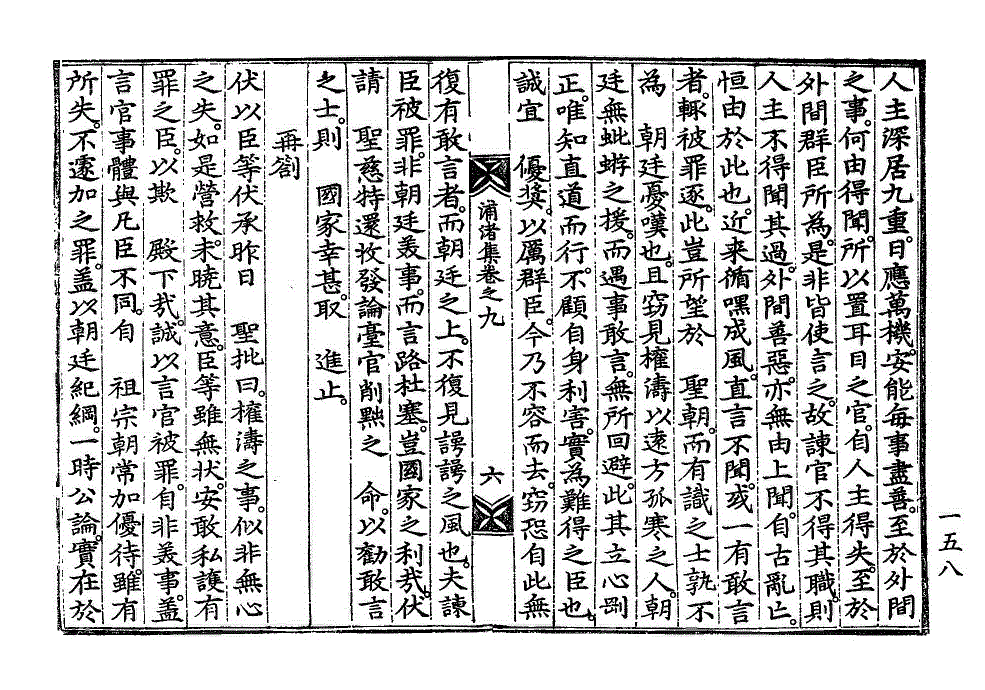 人主深居九重。日应万机。安能每事尽善。至于外间之事。何由得闻。所以置耳目之官。自人主得失。至于外间群臣所为。是非皆使言之。故谏官不得其职。则人主不得闻其过。外间善恶。亦无由上闻。自古乱亡。恒由于此也。近来循嘿成风。直言不闻。或一有敢言者。辄被罪逐。此岂所望于 圣朝。而有识之士孰不为 朝廷忧叹也。且窃见权涛以远方孤寒之人。朝廷无蚍蝣之援。而遇事敢言。无所回避。此其立心刚正。唯知直道而行。不顾自身利害。实为难得之臣也。诚宜 优奖。以厉群臣。今乃不容而去。窃恐自此无复有敢言者。而朝廷之上。不复见谔谔之风也。夫谏臣被罪。非朝廷美事。而言路杜塞。岂国家之利哉。伏请 圣慈特还收发论台官削黜之 命。以劝敢言之士。则 国家幸甚。取 进止。
人主深居九重。日应万机。安能每事尽善。至于外间之事。何由得闻。所以置耳目之官。自人主得失。至于外间群臣所为。是非皆使言之。故谏官不得其职。则人主不得闻其过。外间善恶。亦无由上闻。自古乱亡。恒由于此也。近来循嘿成风。直言不闻。或一有敢言者。辄被罪逐。此岂所望于 圣朝。而有识之士孰不为 朝廷忧叹也。且窃见权涛以远方孤寒之人。朝廷无蚍蝣之援。而遇事敢言。无所回避。此其立心刚正。唯知直道而行。不顾自身利害。实为难得之臣也。诚宜 优奖。以厉群臣。今乃不容而去。窃恐自此无复有敢言者。而朝廷之上。不复见谔谔之风也。夫谏臣被罪。非朝廷美事。而言路杜塞。岂国家之利哉。伏请 圣慈特还收发论台官削黜之 命。以劝敢言之士。则 国家幸甚。取 进止。请还收权涛削黜之 命劄[再劄]
伏以臣等伏承昨日 圣批曰。权涛之事。似非无心之失。如是营救。未晓其意。臣等虽无状。安敢私护有罪之臣。以欺 殿下哉。诚以言官被罪。自非美事。盖言官事体与凡臣不同。自 祖宗朝常加优待。虽有所失。不遽加之罪。盖以朝廷纪纲。一时公论。实在于
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59H 页
 此。若体面轻。则居其职者难以行其志。所以特加优异。使之肆意敢言。无所畏避也。如或其间显有怀奸罔上。谋害善良者。则固当声其罪而斥之。虽施放流之罚。亦无不可。自非然者。无不优容。今权涛之事。不过举劾一善事守令耳。乃是言官职分寻常细微之事也。权涛闻林庆业之事于沈命世。而命世不告其送于某处。则权涛岂有一毫侵及大臣之意哉。况涛与金瑬。初无纤芥之怨。何故辄生倾陷之意哉。虽使涛实有倾陷之意。其事在于金瑬。初非有失。其可以此陷之哉。且台谏职在言事。虽人主过失。犹当极言。况大臣之事。何可不言。自古台谏论宰相者非一也。如使金瑬有可论之罪。则为谏官者。自当暴扬其失而直言之。岂举此微细不可为罪之事。欲动之哉。以此思涛之事。实万万无情也。 殿下不察其情。而遽下削黜之命。非但待台谏之道不当如是。其于举措。为失不细。 君臣之间。情意阻隔。耳目之官。尚不蒙睿察。况疏远之臣哉。此尤深可为叹。且权涛以远方孤踪。素著敢言之节。在于今日。实为难得。今以微细无情之事。被黜而去。臣等窃恐自此台阁寂寥。而为言官者。以言为戒。虽寻常守令之事。皆有所顾忌而
此。若体面轻。则居其职者难以行其志。所以特加优异。使之肆意敢言。无所畏避也。如或其间显有怀奸罔上。谋害善良者。则固当声其罪而斥之。虽施放流之罚。亦无不可。自非然者。无不优容。今权涛之事。不过举劾一善事守令耳。乃是言官职分寻常细微之事也。权涛闻林庆业之事于沈命世。而命世不告其送于某处。则权涛岂有一毫侵及大臣之意哉。况涛与金瑬。初无纤芥之怨。何故辄生倾陷之意哉。虽使涛实有倾陷之意。其事在于金瑬。初非有失。其可以此陷之哉。且台谏职在言事。虽人主过失。犹当极言。况大臣之事。何可不言。自古台谏论宰相者非一也。如使金瑬有可论之罪。则为谏官者。自当暴扬其失而直言之。岂举此微细不可为罪之事。欲动之哉。以此思涛之事。实万万无情也。 殿下不察其情。而遽下削黜之命。非但待台谏之道不当如是。其于举措。为失不细。 君臣之间。情意阻隔。耳目之官。尚不蒙睿察。况疏远之臣哉。此尤深可为叹。且权涛以远方孤踪。素著敢言之节。在于今日。实为难得。今以微细无情之事。被黜而去。臣等窃恐自此台阁寂寥。而为言官者。以言为戒。虽寻常守令之事。皆有所顾忌而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59L 页
 不敢言也。其所损岂不大哉。如使涛有倾陷之心。奸巧之计。则臣等何敢营救。以负 殿下哉。 殿下以臣等为营救。是非但未察权涛之情。亦恐未察臣等之情也。伏乞 圣慈特霁雷霆之威。还收削黜之 命。无使言责之地有覆盆之叹。不胜幸甚。取 进止。
不敢言也。其所损岂不大哉。如使涛有倾陷之心。奸巧之计。则臣等何敢营救。以负 殿下哉。 殿下以臣等为营救。是非但未察权涛之情。亦恐未察臣等之情也。伏乞 圣慈特霁雷霆之威。还收削黜之 命。无使言责之地有覆盆之叹。不胜幸甚。取 进止。请改勘勋劄
伏以人君制治之要。其权唯在赏罚。赏罚得其当则人心服。且有所劝戒。人知趋事而畏罪。治功所以成也。赏罚不得其当则人心不服。庶人议其上。且无所劝戒。人皆惰于职业。而不惮于为非。国之所以陵夷衰替。不复能自振。实由于此也。故古之愿治之君。莫不以赏罚为重。赏必加于有功。而无无功而授者。刑必加于有罪。而无无罪而及者。古之贤君谊辟。所以建立事功。措世治安。皆用是道。然则致治之术。夫岂难哉。唯慎此而已。 国家不幸。逆变继起。而前后论功。皆不能无人言。呜呼。世道之卑污。风俗之不美。于此益可见矣。台谏或削或改之请。实国人公共之论也。而论执既久。未蒙 允俞。此臣等之所未晓也。夫元克諴擒贼之时。辛庆英,李胤男等。或到前街。或到前川。皆未及焉。夫所谓功者。谓其捉贼也。捉贼之时。
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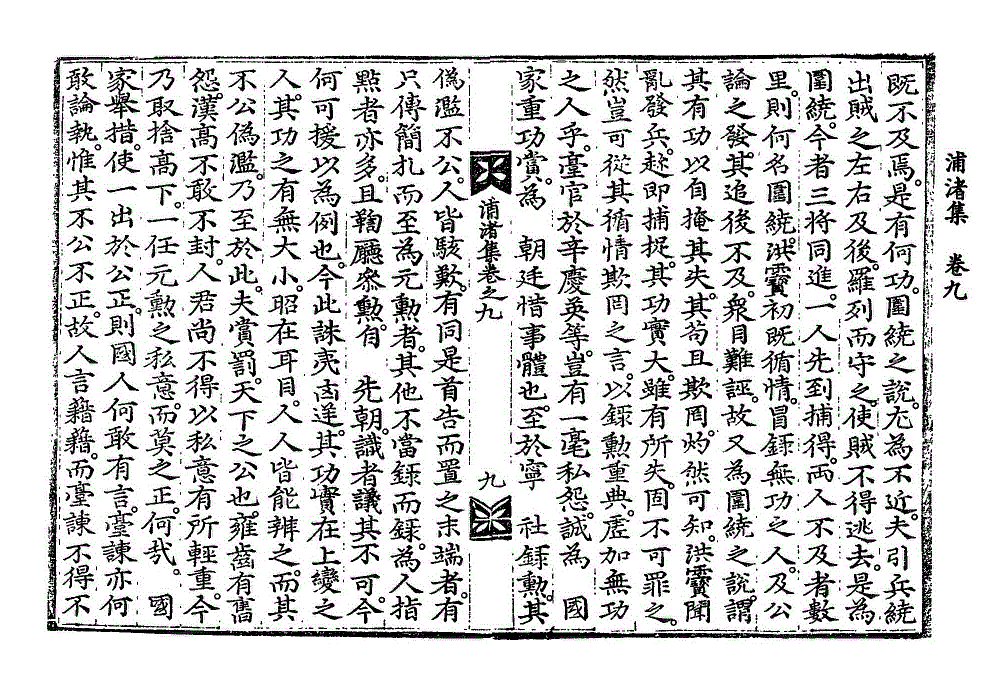 既不及焉。是有何功。围绕之说。尤为不近。夫引兵绕出贼之左右及后。罗列而守之。使贼不得逃去。是为围绕。今者三将同进。一人先到捕得。两人不及者数里。则何名围绕。洪宝初既循情。冒录无功之人。及公论之发。其追后不及。众目难诬。故又为围绕之说。谓其有功以自掩其失。其苟且欺罔。灼然可知。洪宝闻乱发兵。趁即捕捉。其功实大。虽有所失。固不可罪之。然岂可从其循情欺罔之言。以录勋重典。虚加无功之人乎。台官于辛庆英等。岂有一毫私怨。诚为 国家重功赏。为 朝廷惜事体也。至于宁 社录勋。其伪滥不公。人皆骇叹。有同是首告而置之末端者。有只传简札而至为元勋者。其他不当录而录。为人指点者亦多。且鞫厅参勋。自 先朝。识者议其不可。今何可援以为例也。今此诛夷凶逆。其功实在上变之人。其功之有无大小。昭在耳目。人人皆能辨之。而其不公伪滥。乃至于此。夫赏罚。天下之公也。雍齿有旧怨。汉高不敢不封。人君尚不得以私意有所轻重。今乃取舍高下。一任元勋之私意。而莫之正。何哉。 国家举措。使一出于公正。则国人何敢有言。台谏亦何敢论执。惟其不公不正。故人言藉藉。而台谏不得不
既不及焉。是有何功。围绕之说。尤为不近。夫引兵绕出贼之左右及后。罗列而守之。使贼不得逃去。是为围绕。今者三将同进。一人先到捕得。两人不及者数里。则何名围绕。洪宝初既循情。冒录无功之人。及公论之发。其追后不及。众目难诬。故又为围绕之说。谓其有功以自掩其失。其苟且欺罔。灼然可知。洪宝闻乱发兵。趁即捕捉。其功实大。虽有所失。固不可罪之。然岂可从其循情欺罔之言。以录勋重典。虚加无功之人乎。台官于辛庆英等。岂有一毫私怨。诚为 国家重功赏。为 朝廷惜事体也。至于宁 社录勋。其伪滥不公。人皆骇叹。有同是首告而置之末端者。有只传简札而至为元勋者。其他不当录而录。为人指点者亦多。且鞫厅参勋。自 先朝。识者议其不可。今何可援以为例也。今此诛夷凶逆。其功实在上变之人。其功之有无大小。昭在耳目。人人皆能辨之。而其不公伪滥。乃至于此。夫赏罚。天下之公也。雍齿有旧怨。汉高不敢不封。人君尚不得以私意有所轻重。今乃取舍高下。一任元勋之私意。而莫之正。何哉。 国家举措。使一出于公正。则国人何敢有言。台谏亦何敢论执。惟其不公不正。故人言藉藉。而台谏不得不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0L 页
 论执。 殿下不恤国人之言。不听台谏之论。欲以其不公不正之勋籍。因以不改。录勋是何等举措。是 殿下于此大举措。不恶其不公不正。而不欲其必于公正也。臣等窃不胜忧闷焉。夫治乱二字之义。指何事而言欤。所谓治者。自朝廷之上。是非真伪。明白辨析。是者行而非者遏。真者用而伪者息。凡所举措施为无不真实。是当如是而后人心悦服。而事皆得当。人皆得所矣。是之谓治也。若是非紊乱。真伪混杂。则何事得其当。何民得其所乎。此之谓乱也。然则治乱之分。只在朝廷之上是非真伪辨别与混殽而已。今此录勋。其是非真伪。混殽莫甚。此莫重之举措如是。而不正之。则何事不如是乎。每事如是则 国家安得不乱。故臣等窃以为今此勋籍。正之与否。实治乱兴亡之所由分也。诚能于此分明辨别。使虚伪不得乱真。取舍一于公正。而又因此而推之。凡事皆然。至于所行皆是。所为皆实。则人心翕服而百事脩举。生民可得以安。国势可得以固。何忧乎乱逆。何忧乎夷狄。今乃不然。任其混殽。不欲正之。臣等窃恐陵夷衰替。不复能自振。从此而始也。且今此所录。真是公正。无有伪滥。则台谏之言。未必是国人公共之论。 殿
论执。 殿下不恤国人之言。不听台谏之论。欲以其不公不正之勋籍。因以不改。录勋是何等举措。是 殿下于此大举措。不恶其不公不正。而不欲其必于公正也。臣等窃不胜忧闷焉。夫治乱二字之义。指何事而言欤。所谓治者。自朝廷之上。是非真伪。明白辨析。是者行而非者遏。真者用而伪者息。凡所举措施为无不真实。是当如是而后人心悦服。而事皆得当。人皆得所矣。是之谓治也。若是非紊乱。真伪混杂。则何事得其当。何民得其所乎。此之谓乱也。然则治乱之分。只在朝廷之上是非真伪辨别与混殽而已。今此录勋。其是非真伪。混殽莫甚。此莫重之举措如是。而不正之。则何事不如是乎。每事如是则 国家安得不乱。故臣等窃以为今此勋籍。正之与否。实治乱兴亡之所由分也。诚能于此分明辨别。使虚伪不得乱真。取舍一于公正。而又因此而推之。凡事皆然。至于所行皆是。所为皆实。则人心翕服而百事脩举。生民可得以安。国势可得以固。何忧乎乱逆。何忧乎夷狄。今乃不然。任其混殽。不欲正之。臣等窃恐陵夷衰替。不复能自振。从此而始也。且今此所录。真是公正。无有伪滥。则台谏之言。未必是国人公共之论。 殿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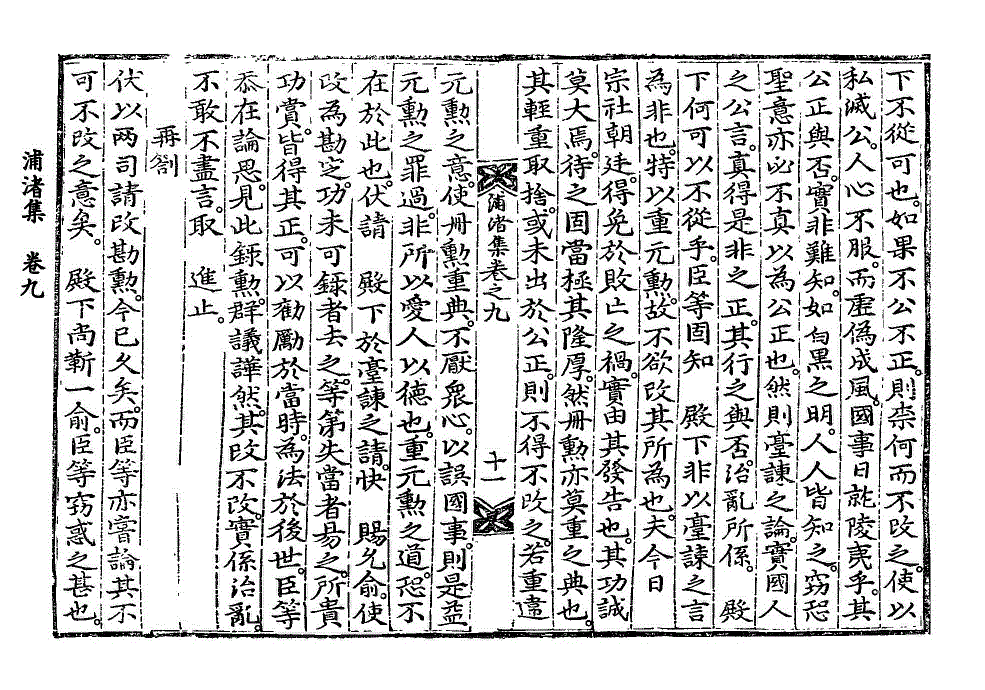 下不从可也。如果不公不正。则柰何而不改之。使以私灭公。人心不服。而虚伪成风。国事日就陵夷乎。其公正与否。实非难知。如白黑之明。人人皆知之。窃恐圣意亦必不真以为公正也。然则台谏之论。实国人之公言。真得是非之正。其行之与否。治乱所系。 殿下何可以不从乎。臣等固知 殿下非以台谏之言为非也。特以重元勋。故不欲改其所为也。夫今日 宗社朝廷。得免于败亡之祸。实由其发告也。其功诚莫大焉。待之固当极其隆厚。然册勋亦莫重之典也。其轻重取舍。或未出于公正。则不得不改之。若重违元勋之意。使册勋重典。不厌众心。以误国事。则是益元勋之罪过。非所以爱人以德也。重元勋之道。恐不在于此也。伏请 殿下于台谏之请。快 赐允俞。使改为勘定。功未可录者去之。等第失当者易之。所贵功赏。皆得其正。可以劝励于当时。为法于后世。臣等忝在论思。见此录勋。群议哗然。其改不改。实系治乱。不敢不尽言。取 进止。
下不从可也。如果不公不正。则柰何而不改之。使以私灭公。人心不服。而虚伪成风。国事日就陵夷乎。其公正与否。实非难知。如白黑之明。人人皆知之。窃恐圣意亦必不真以为公正也。然则台谏之论。实国人之公言。真得是非之正。其行之与否。治乱所系。 殿下何可以不从乎。臣等固知 殿下非以台谏之言为非也。特以重元勋。故不欲改其所为也。夫今日 宗社朝廷。得免于败亡之祸。实由其发告也。其功诚莫大焉。待之固当极其隆厚。然册勋亦莫重之典也。其轻重取舍。或未出于公正。则不得不改之。若重违元勋之意。使册勋重典。不厌众心。以误国事。则是益元勋之罪过。非所以爱人以德也。重元勋之道。恐不在于此也。伏请 殿下于台谏之请。快 赐允俞。使改为勘定。功未可录者去之。等第失当者易之。所贵功赏。皆得其正。可以劝励于当时。为法于后世。臣等忝在论思。见此录勋。群议哗然。其改不改。实系治乱。不敢不尽言。取 进止。请改勘勋劄[再劄]
伏以两司请改勘勋。今已久矣。而臣等亦尝论其不可不改之意矣。 殿下尚靳一俞。臣等窃惑之甚也。
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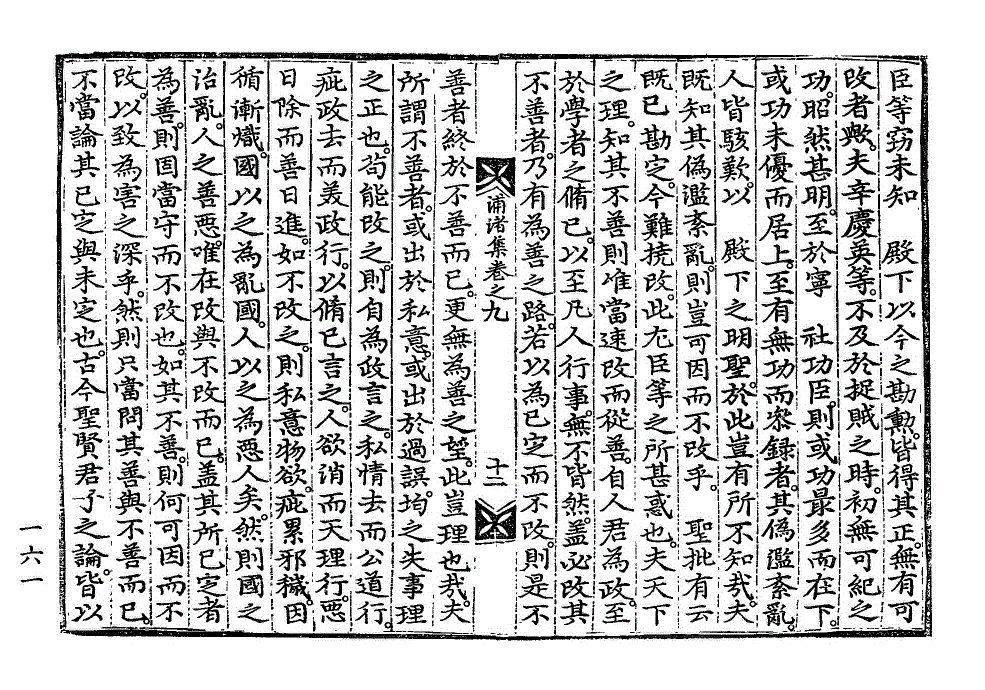 臣等窃未知 殿下以今之勘勋。皆得其正。无有可改者欤。夫辛庆英等。不及于捉贼之时。初无可纪之功。昭然甚明。至于宁 社功臣。则或功最多而在下。或功未优而居上。至有无功而参录者。其伪滥紊乱。人皆骇叹。以 殿下之明圣。于此岂有所不知哉。夫既知其伪滥紊乱。则岂可因而不改乎。 圣批有云既已勘定。今难挠改。此尤臣等之所甚惑也。夫天下之理。知其不善则唯当速改而从善。自人君为政。至于学者之脩己。以至凡人行事。无不皆然。盖必改其不善者。乃有为善之路。若以为已定而不改。则是不善者终于不善而已。更无为善之望。此岂理也哉。夫所谓不善者。或出于私意。或出于过误。均之失事理之正也。苟能改之。则自为政言之。私情去而公道行。疵政去而美政行。以脩己言之。人欲消而天理行。恶日除而善日进。如不改之。则私意物欲。疵累邪秽。因循渐炽。国以之为乱国。人以之为恶人矣。然则国之治乱。人之善恶。唯在改与不改而已。盖其所已定者为善。则固当守而不改也。如其不善。则何可因而不改。以致为害之深乎。然则只当问其善与不善而已。不当论其已定与未定也。古今圣贤君子之论。皆以
臣等窃未知 殿下以今之勘勋。皆得其正。无有可改者欤。夫辛庆英等。不及于捉贼之时。初无可纪之功。昭然甚明。至于宁 社功臣。则或功最多而在下。或功未优而居上。至有无功而参录者。其伪滥紊乱。人皆骇叹。以 殿下之明圣。于此岂有所不知哉。夫既知其伪滥紊乱。则岂可因而不改乎。 圣批有云既已勘定。今难挠改。此尤臣等之所甚惑也。夫天下之理。知其不善则唯当速改而从善。自人君为政。至于学者之脩己。以至凡人行事。无不皆然。盖必改其不善者。乃有为善之路。若以为已定而不改。则是不善者终于不善而已。更无为善之望。此岂理也哉。夫所谓不善者。或出于私意。或出于过误。均之失事理之正也。苟能改之。则自为政言之。私情去而公道行。疵政去而美政行。以脩己言之。人欲消而天理行。恶日除而善日进。如不改之。则私意物欲。疵累邪秽。因循渐炽。国以之为乱国。人以之为恶人矣。然则国之治乱。人之善恶。唯在改与不改而已。盖其所已定者为善。则固当守而不改也。如其不善。则何可因而不改。以致为害之深乎。然则只当问其善与不善而已。不当论其已定与未定也。古今圣贤君子之论。皆以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2H 页
 不善能改为善。未尝闻以已定不改为善也。如果以已定不改为善也。则易何以曰。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孔子何以曰。过则勿惮改。孟子何以曰。如知其非义。则斯速已矣。 殿下以已定而不可改为教。臣等窃恐此 殿下所见未免有差处也。凡行事之得失。皆由于所见之得失。所见既差。则随其大小。无不为害。古之圣贤。必以致知为先务。而又必以格君心之非。为事君之要道者。诚以此也。臣等窃见 殿下于凡事。每以已定不可改为定守。夫已定而不改。以常情言之。则可谓固守矣。然所贵于固守者。谓其择善而固守也。若不问善与不善。徒以已定而固守。则岂不为害。况乎知其不善。而固守不变。则其为害又何可胜言哉。故臣等窃以为此 殿下所见之差处。而必改此所见。而后其于治道。乃有可望矣。以 殿下之仁圣。于 圣躬少无失德。而治效未著。反忧国事之日非者。未必不由于此也。今此勘勋。实 国家莫大举措。岂不欲其至正至公无一毫可议也。如果得其公正无可议之事则不改可也。今其不公不正。人皆骇愤。如是而徒以已定而不改。非臣等之所敢知也。夫已定之失。诚不可改。则虽其事立致败亡者。亦当
不善能改为善。未尝闻以已定不改为善也。如果以已定不改为善也。则易何以曰。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孔子何以曰。过则勿惮改。孟子何以曰。如知其非义。则斯速已矣。 殿下以已定而不可改为教。臣等窃恐此 殿下所见未免有差处也。凡行事之得失。皆由于所见之得失。所见既差。则随其大小。无不为害。古之圣贤。必以致知为先务。而又必以格君心之非。为事君之要道者。诚以此也。臣等窃见 殿下于凡事。每以已定不可改为定守。夫已定而不改。以常情言之。则可谓固守矣。然所贵于固守者。谓其择善而固守也。若不问善与不善。徒以已定而固守。则岂不为害。况乎知其不善。而固守不变。则其为害又何可胜言哉。故臣等窃以为此 殿下所见之差处。而必改此所见。而后其于治道。乃有可望矣。以 殿下之仁圣。于 圣躬少无失德。而治效未著。反忧国事之日非者。未必不由于此也。今此勘勋。实 国家莫大举措。岂不欲其至正至公无一毫可议也。如果得其公正无可议之事则不改可也。今其不公不正。人皆骇愤。如是而徒以已定而不改。非臣等之所敢知也。夫已定之失。诚不可改。则虽其事立致败亡者。亦当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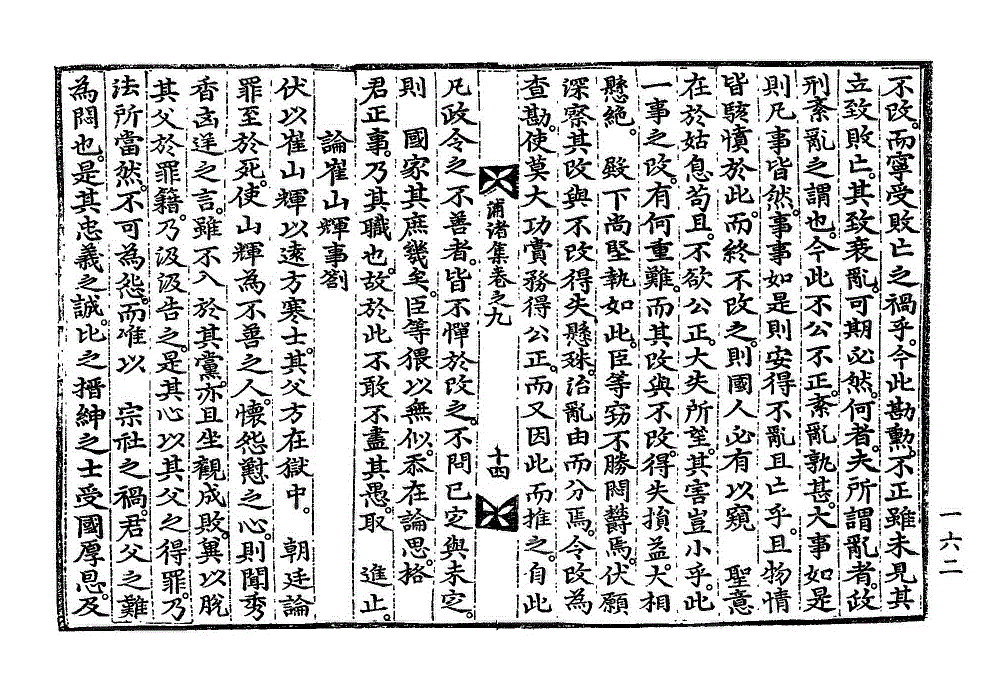 不改。而宁受败亡之祸乎。今此勘勋。不正虽未见其立致败亡。其致衰乱。可期必然。何者。夫所谓乱者。政刑紊乱之谓也。今此不公不正。紊乱孰甚。大事如是则凡事皆然。事事如是则安得不乱且亡乎。且物情皆骇愤于此。而终不改之。则国人必有以窥 圣意在于姑息苟且。不欲公正。大失所望。其害岂小乎。此一事之改。有何重难。而其改与不改。得失损益。大相悬绝。 殿下尚坚执如此。臣等窃不胜闷郁焉。伏愿深察其改与不改得失悬殊。治乱由而分焉。令改为查勘。使莫大功赏务得公正。而又因此而推之。自此凡政令之不善者。皆不惮于改之。不问已定与未定。则 国家其庶几矣。臣等猥以无似。忝在论思。格 君正事。乃其职也。故于此不敢不尽其愚。取 进止。
不改。而宁受败亡之祸乎。今此勘勋。不正虽未见其立致败亡。其致衰乱。可期必然。何者。夫所谓乱者。政刑紊乱之谓也。今此不公不正。紊乱孰甚。大事如是则凡事皆然。事事如是则安得不乱且亡乎。且物情皆骇愤于此。而终不改之。则国人必有以窥 圣意在于姑息苟且。不欲公正。大失所望。其害岂小乎。此一事之改。有何重难。而其改与不改。得失损益。大相悬绝。 殿下尚坚执如此。臣等窃不胜闷郁焉。伏愿深察其改与不改得失悬殊。治乱由而分焉。令改为查勘。使莫大功赏务得公正。而又因此而推之。自此凡政令之不善者。皆不惮于改之。不问已定与未定。则 国家其庶几矣。臣等猥以无似。忝在论思。格 君正事。乃其职也。故于此不敢不尽其愚。取 进止。论崔山辉事劄
伏以崔山辉以远方寒士。其父方在狱中。 朝廷论罪至于死。使山辉为不善之人。怀怨怼之心。则闻秀香凶逆之言。虽不入于其党。亦且坐观成败。冀以脱其父于罪籍。乃汲汲告之。是其心以其父之得罪。乃法所当然。不可为怨。而唯以 宗社之祸。君父之难为闷也。是其忠义之诚。比之搢绅之士受国厚恩。及
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3H 页
 无罪责者。可谓百倍。诚宜 特加优宠。以奖其善。且山辉所告之贼。皆是其中巨魁腹心。则其功亦岂少哉。或以其迟告为罪。此则大不然。夫山辉闻秀香之言。在人定之后。其时夜禁甚严。人定后不得往来。待闻晓钟。奔告金澃。使言于沈命世。乃是即告。不可为迟也。山辉之使言于沈命世。欲命世 上达也。以汉时张章,董忠等告霍禹之事观之。则命世自当 上达。不当还使山辉自告也。然则虽曰迟告。乃命世之迟也。非山辉之迟也。故臣等窃以为山辉善则最大。而罪则无也。自山辉上变。两司停其父晛按法之 启。乃嘉山辉之善也。然晛因流六镇极边之地。夫晛之罪。以法言之。则虽死不为过。流窜之罚。亦以情恕也。然山辉之善。足以免其父之罪。则窃恐赦之为宜也。夫 国家待功臣。与之同带砺之盟。载铁券之书。赐功勋之号。尊其爵富其家。所以宠异其善。使享永久之福也。今以山辉之情言之。虽尊官厚禄。极人臣之荣。乐莫如免其父之罪也。然则宠待山辉之道。莫如赦其父也。昔淳于意有罪当刑。缇萦一言。汉文诏除之。今山辉之善。非如缇萦之一言。且国法宥功臣子孙。至于原从亦然。 恩泽可谓至厚矣。夫子孙累
无罪责者。可谓百倍。诚宜 特加优宠。以奖其善。且山辉所告之贼。皆是其中巨魁腹心。则其功亦岂少哉。或以其迟告为罪。此则大不然。夫山辉闻秀香之言。在人定之后。其时夜禁甚严。人定后不得往来。待闻晓钟。奔告金澃。使言于沈命世。乃是即告。不可为迟也。山辉之使言于沈命世。欲命世 上达也。以汉时张章,董忠等告霍禹之事观之。则命世自当 上达。不当还使山辉自告也。然则虽曰迟告。乃命世之迟也。非山辉之迟也。故臣等窃以为山辉善则最大。而罪则无也。自山辉上变。两司停其父晛按法之 启。乃嘉山辉之善也。然晛因流六镇极边之地。夫晛之罪。以法言之。则虽死不为过。流窜之罚。亦以情恕也。然山辉之善。足以免其父之罪。则窃恐赦之为宜也。夫 国家待功臣。与之同带砺之盟。载铁券之书。赐功勋之号。尊其爵富其家。所以宠异其善。使享永久之福也。今以山辉之情言之。虽尊官厚禄。极人臣之荣。乐莫如免其父之罪也。然则宠待山辉之道。莫如赦其父也。昔淳于意有罪当刑。缇萦一言。汉文诏除之。今山辉之善。非如缇萦之一言。且国法宥功臣子孙。至于原从亦然。 恩泽可谓至厚矣。夫子孙累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3L 页
 世。犹且宥及。况其父而不得免乎。山辉随父北行。作旅边陲。孑孑孤寄。恐非所以优待有大功之人也。今山辉幸蒙 天恩。得厕朝籍。伏请 殿下特赦崔晛之罪。召山辉以驲骑。使与其父偕来。则非但山辉父子感激 恩宠。灭身无以仰报。凡在瞻聆。莫不感动。知 朝廷待为善之人如是其厚。而为善之报。可以及于其亲。皆思勉于忠义矣。臣等于山辉。绝无相识之分。诚以其善可嘉。其功甚大。 朝廷待之。特宜优厚。以劝人之忠。恐或以庸臣遇之。使人心落莫。不敢不言。取 进止。
世。犹且宥及。况其父而不得免乎。山辉随父北行。作旅边陲。孑孑孤寄。恐非所以优待有大功之人也。今山辉幸蒙 天恩。得厕朝籍。伏请 殿下特赦崔晛之罪。召山辉以驲骑。使与其父偕来。则非但山辉父子感激 恩宠。灭身无以仰报。凡在瞻聆。莫不感动。知 朝廷待为善之人如是其厚。而为善之报。可以及于其亲。皆思勉于忠义矣。臣等于山辉。绝无相识之分。诚以其善可嘉。其功甚大。 朝廷待之。特宜优厚。以劝人之忠。恐或以庸臣遇之。使人心落莫。不敢不言。取 进止。论兵曹判书李贵劄 批未安劄(己巳)
伏以臣等伏见顷日 答兵曹判书李贵劄子。曰。群而不党。孔子格言。割烹要汤。伊尹短处。以此观之。则朱子之言。不能无弊也。大抵君子之处身。遇则行道。不遇则耕野而已。若有一毫有所为之心。则便非天理也。其后再劄之答。又曰。古昔圣贤嘉言至论。不为不多。择其无弊者而行之可也。臣等窃恐 殿下犹未能深究前贤言意之所在。而遽断之以为有弊。至形诸言语。夫如是则非惟察理疏略。其于圣贤之旨。义理之实。未能究极其所归。又不免有轻忽圣贤之
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4H 页
 失。凡圣贤格言至论。苟吾见之所未到。而于吾心有未当者。则皆可诿之为未尽。弃之而不察。其害于事岂小哉。臣等请先论党字之义。以及于朱子之旨。夫党之为字。本同类之称。如乡党母党妻党之云。未必有私党之意。然古人以私相阿比者谓之党。如陈司败谓君子不党。孔子曰。群而不党。是也。盖人之于世。必有相合者。而其合也各以其类。君子与君子合。则其所取者义也。故平居则相资而修己。立朝则协心而辅世。小人与小人合。则其所取者利也。故其所盘结而相助者。不顾事之是非。只图为己利而已。故古人谓君子曰朋。以其公也。小人曰党。以其私也。然则党之为字。乃私相盘结之名。而不可称之于君子也。然则党是小人之事。人臣之有私党。国家之大害也。人主之所必恶也。故谗人陷君子者。必目之为党。以激怒其君而售其网打之计。盖君子之与君子交也。亦更相还往。更相论议。更相推荐。虽其相与之意。及其所为之事。与小人之为党者。公私之分。迥然不同。而其迹则亦相似也。彼为谗者。因其疑似而激怒之。故其谗易入而其听易惑也。如前汉以萧望之,刘更生等为党。后汉以李膺,杜密之徒为党。及宋之元祐。
失。凡圣贤格言至论。苟吾见之所未到。而于吾心有未当者。则皆可诿之为未尽。弃之而不察。其害于事岂小哉。臣等请先论党字之义。以及于朱子之旨。夫党之为字。本同类之称。如乡党母党妻党之云。未必有私党之意。然古人以私相阿比者谓之党。如陈司败谓君子不党。孔子曰。群而不党。是也。盖人之于世。必有相合者。而其合也各以其类。君子与君子合。则其所取者义也。故平居则相资而修己。立朝则协心而辅世。小人与小人合。则其所取者利也。故其所盘结而相助者。不顾事之是非。只图为己利而已。故古人谓君子曰朋。以其公也。小人曰党。以其私也。然则党之为字。乃私相盘结之名。而不可称之于君子也。然则党是小人之事。人臣之有私党。国家之大害也。人主之所必恶也。故谗人陷君子者。必目之为党。以激怒其君而售其网打之计。盖君子之与君子交也。亦更相还往。更相论议。更相推荐。虽其相与之意。及其所为之事。与小人之为党者。公私之分。迥然不同。而其迹则亦相似也。彼为谗者。因其疑似而激怒之。故其谗易入而其听易惑也。如前汉以萧望之,刘更生等为党。后汉以李膺,杜密之徒为党。及宋之元祐。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4L 页
 伪学道学之类是也。以是。君子之朋。亦谓之党也。然则所谓君子之党。乃正人以义相合者也。非若小人之私党也。与孔子所谓群而不党。其义自不同也。如汉之萧,刘,李,杜诸贤。固皆一时之正士。至于宋之大贤如程朱。亦不免指为党人。岂可谓其为党而非君子也。为人君者。诚能信任君子之党。勿为谗邪所间。而使得尽其展效。则群贤布列。众职修举。自能措世于治平。古之圣帝明王所以致治。其道不过如是而已。如欧阳脩之论。以尧舜之八元,八凯,皋,夔,稷,契二十二人。武王之臣三千人为朋。君子之朋之验是也。然则古昔帝王。用君子之党而治。后世庸主。斥君子之党而乱。此诚往事之明鉴也。当朱子之时。阴邪盘结于内。而士大夫之嗜利者。争相附会。指善类为党。是时留正为宰相。不能辨其贤邪而进退之。反恐有忤于群小。而其身自陷于君子之党。至以善类之有党为忧。朱子深言君子之党不可疾也。故其言曰。不惟不疾君子之党。而不惮以身为之党。不惟不惮以身为之党。而又将引其君以为党而不惮也。此言实与古昔圣人之言。若合符契。如舜之言曰。臣哉邻哉。邻哉臣哉。又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夫与之为邻。与之
伪学道学之类是也。以是。君子之朋。亦谓之党也。然则所谓君子之党。乃正人以义相合者也。非若小人之私党也。与孔子所谓群而不党。其义自不同也。如汉之萧,刘,李,杜诸贤。固皆一时之正士。至于宋之大贤如程朱。亦不免指为党人。岂可谓其为党而非君子也。为人君者。诚能信任君子之党。勿为谗邪所间。而使得尽其展效。则群贤布列。众职修举。自能措世于治平。古之圣帝明王所以致治。其道不过如是而已。如欧阳脩之论。以尧舜之八元,八凯,皋,夔,稷,契二十二人。武王之臣三千人为朋。君子之朋之验是也。然则古昔帝王。用君子之党而治。后世庸主。斥君子之党而乱。此诚往事之明鉴也。当朱子之时。阴邪盘结于内。而士大夫之嗜利者。争相附会。指善类为党。是时留正为宰相。不能辨其贤邪而进退之。反恐有忤于群小。而其身自陷于君子之党。至以善类之有党为忧。朱子深言君子之党不可疾也。故其言曰。不惟不疾君子之党。而不惮以身为之党。不惟不惮以身为之党。而又将引其君以为党而不惮也。此言实与古昔圣人之言。若合符契。如舜之言曰。臣哉邻哉。邻哉臣哉。又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夫与之为邻。与之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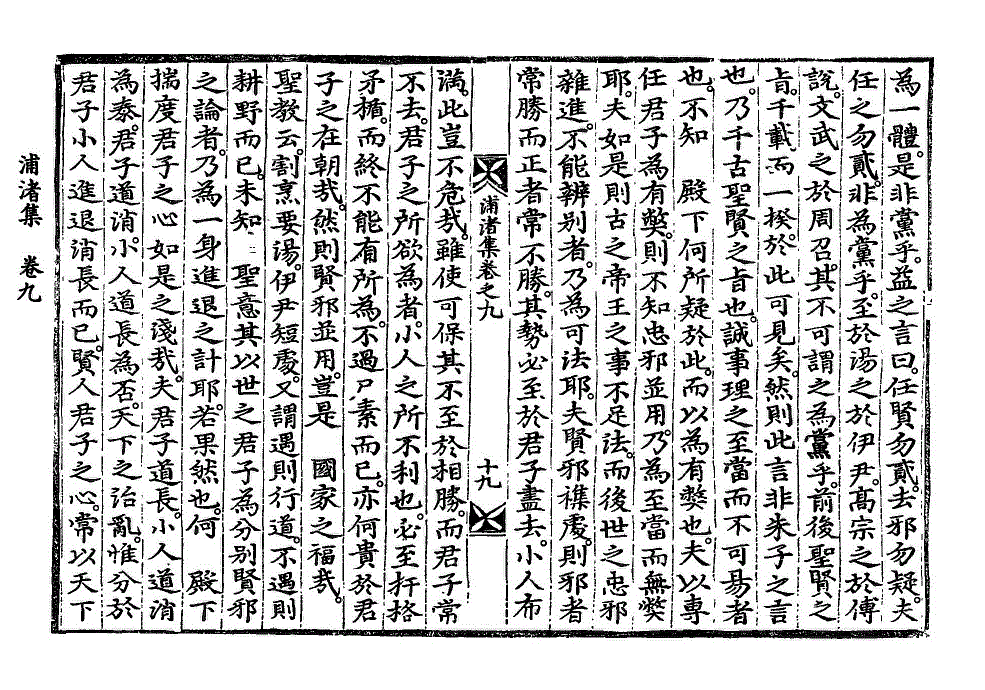 为一体。是非党乎。益之言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夫任之勿贰。非为党乎。至于汤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说。文武之于周召。其不可谓之为党乎。前后圣贤之旨。千载而一揆。于此可见矣。然则此言非朱子之言也。乃千古圣贤之旨也。诚事理之至当而不可易者也。不知 殿下何所疑于此。而以为有弊也。夫以专任君子为有弊。则不知忠邪并用。乃为至当而无弊耶。夫如是则古之帝王之事不足法。而后世之忠邪杂进。不能辨别者。乃为可法耶。夫贤邪杂处。则邪者常胜而正者常不胜。其势必至于君子尽去。小人布满。此岂不危哉。虽使可保其不至于相胜。而君子常不去。君子之所欲为者。小人之所不利也。必至捍格矛楯。而终不能有所为。不过尸素而已。亦何贵于君子之在朝哉。然则贤邪并用。岂是 国家之福哉。 圣教云。割烹要汤。伊尹短处。又谓遇则行道。不遇则耕野而已。未知 圣意其以世之君子为分别贤邪之论者。乃为一身进退之计耶。若果然也。何 殿下揣度君子之心如是之浅哉。夫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为泰。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为否。天下之治乱。惟分于君子小人进退消长而已。贤人君子之心。常以天下
为一体。是非党乎。益之言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夫任之勿贰。非为党乎。至于汤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说。文武之于周召。其不可谓之为党乎。前后圣贤之旨。千载而一揆。于此可见矣。然则此言非朱子之言也。乃千古圣贤之旨也。诚事理之至当而不可易者也。不知 殿下何所疑于此。而以为有弊也。夫以专任君子为有弊。则不知忠邪并用。乃为至当而无弊耶。夫如是则古之帝王之事不足法。而后世之忠邪杂进。不能辨别者。乃为可法耶。夫贤邪杂处。则邪者常胜而正者常不胜。其势必至于君子尽去。小人布满。此岂不危哉。虽使可保其不至于相胜。而君子常不去。君子之所欲为者。小人之所不利也。必至捍格矛楯。而终不能有所为。不过尸素而已。亦何贵于君子之在朝哉。然则贤邪并用。岂是 国家之福哉。 圣教云。割烹要汤。伊尹短处。又谓遇则行道。不遇则耕野而已。未知 圣意其以世之君子为分别贤邪之论者。乃为一身进退之计耶。若果然也。何 殿下揣度君子之心如是之浅哉。夫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为泰。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为否。天下之治乱。惟分于君子小人进退消长而已。贤人君子之心。常以天下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5L 页
 之治乱安危为念。其忧天下。甚于己之私。自昔圣贤。遑遑汲汲。不避勤苦。死而后已者。只是为斯民耳。其用心如是。则其于安危之几。岂忍坐视而莫之救哉。然则其必欲进贤退邪者。只是为天下生灵计也。岂有一毫私意哉。伊尹之割烹。孟子已辨其不然。此乃当时鄙野之人无识之语耳。非伊尹实有此事也。虽有任底意思。与孔子小异。其所自任者。乃天下之重也。岂是为一身之计哉。至于朱子。则平生静退。每有除命。无不恳辞。或踰年而不受。其立朝仅四十六日。耕野乃其一生所为。岂惮于耕野而为此论哉。圣贤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则其忧世之深。救世之急。岂可谓之非天理也哉。且君子之仕。不合则去。乃其进退之正也。故苟明知其不可留。则虽留之。不敢不去。况人主以耕野责其臣。则苟有廉耻者。谁敢不思其退去。贤士进退。安危所系。古之人君。贵德而尊士。谏则必行。言则必听。唯恐贤者有所不合而去。今 殿下此言。则不欲为君子之党。而宁使君子不遇而去。窃恐孟子所谓訑訑之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者。不幸而近之也。然今之所谓党者则异于是。盖未是一边皆君子。一边皆小人。各有善人焉。各有不
之治乱安危为念。其忧天下。甚于己之私。自昔圣贤。遑遑汲汲。不避勤苦。死而后已者。只是为斯民耳。其用心如是。则其于安危之几。岂忍坐视而莫之救哉。然则其必欲进贤退邪者。只是为天下生灵计也。岂有一毫私意哉。伊尹之割烹。孟子已辨其不然。此乃当时鄙野之人无识之语耳。非伊尹实有此事也。虽有任底意思。与孔子小异。其所自任者。乃天下之重也。岂是为一身之计哉。至于朱子。则平生静退。每有除命。无不恳辞。或踰年而不受。其立朝仅四十六日。耕野乃其一生所为。岂惮于耕野而为此论哉。圣贤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则其忧世之深。救世之急。岂可谓之非天理也哉。且君子之仕。不合则去。乃其进退之正也。故苟明知其不可留。则虽留之。不敢不去。况人主以耕野责其臣。则苟有廉耻者。谁敢不思其退去。贤士进退。安危所系。古之人君。贵德而尊士。谏则必行。言则必听。唯恐贤者有所不合而去。今 殿下此言。则不欲为君子之党。而宁使君子不遇而去。窃恐孟子所谓訑訑之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者。不幸而近之也。然今之所谓党者则异于是。盖未是一边皆君子。一边皆小人。各有善人焉。各有不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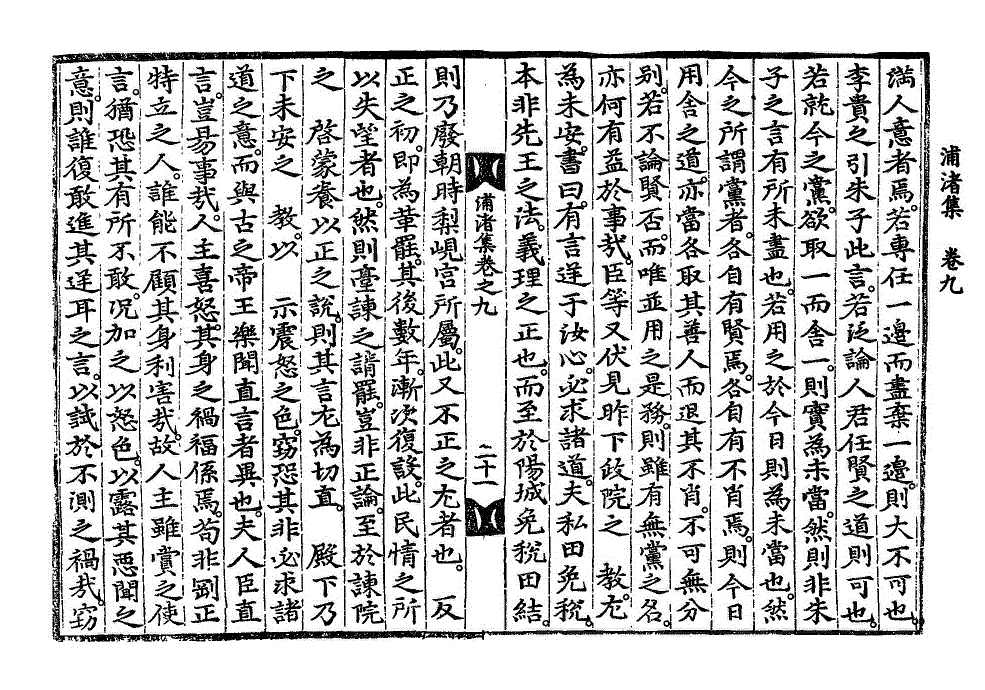 满人意者焉。若专任一边而尽弃一边。则大不可也。李贵之引朱子此言。若泛论人君任贤之道则可也。若就今之党。欲取一而舍一。则实为未当。然则非朱子之言有所未尽也。若用之于今日则为未当也。然今之所谓党者。各自有贤焉。各自有不肖焉。则今日用舍之道。亦当各取其善人而退其不肖。不可无分别。若不论贤否。而唯并用之是务。则虽有无党之名。亦何有益于事哉。臣等又伏见昨下政院之 教。尤为未安。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夫私田免税。本非先王之法。义理之正也。而至于阳城免税田结。则乃废朝时梨岘宫所属。此又不正之尤者也。 反正之初。即为革罢。其后数年。渐次复设。此民情之所以失望者也。然则台谏之请罢。岂非正论。至于谏院之 启蒙养以正之说。则其言尤为切直。 殿下乃下未安之 教。以 示震怒之色。窃恐其非必求诸道之意。而与古之帝王乐闻直言者异也。夫人臣直言。岂易事哉。人主喜怒。其身之祸福系焉。苟非刚正特立之人。谁能不顾其身利害哉。故人主虽赏之使言。犹恐其有所不敢。况加之以怒色。以露其恶闻之意。则谁复敢进其逆耳之言。以试于不测之祸哉。窃
满人意者焉。若专任一边而尽弃一边。则大不可也。李贵之引朱子此言。若泛论人君任贤之道则可也。若就今之党。欲取一而舍一。则实为未当。然则非朱子之言有所未尽也。若用之于今日则为未当也。然今之所谓党者。各自有贤焉。各自有不肖焉。则今日用舍之道。亦当各取其善人而退其不肖。不可无分别。若不论贤否。而唯并用之是务。则虽有无党之名。亦何有益于事哉。臣等又伏见昨下政院之 教。尤为未安。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夫私田免税。本非先王之法。义理之正也。而至于阳城免税田结。则乃废朝时梨岘宫所属。此又不正之尤者也。 反正之初。即为革罢。其后数年。渐次复设。此民情之所以失望者也。然则台谏之请罢。岂非正论。至于谏院之 启蒙养以正之说。则其言尤为切直。 殿下乃下未安之 教。以 示震怒之色。窃恐其非必求诸道之意。而与古之帝王乐闻直言者异也。夫人臣直言。岂易事哉。人主喜怒。其身之祸福系焉。苟非刚正特立之人。谁能不顾其身利害哉。故人主虽赏之使言。犹恐其有所不敢。况加之以怒色。以露其恶闻之意。则谁复敢进其逆耳之言。以试于不测之祸哉。窃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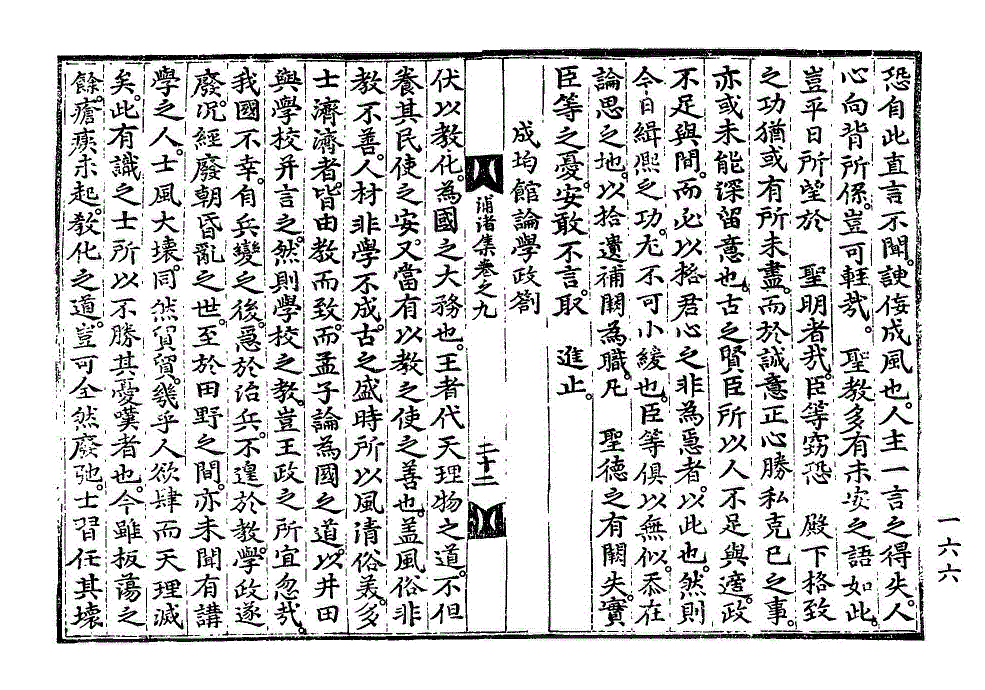 恐自此直言不闻。谀佞成风也。人主一言之得失。人心向背所系。岂可轻哉。 圣教多有未安之语如此。岂平日所望于 圣明者哉。臣等窃恐 殿下格致之功犹或有所未尽。而于诚意正心胜私克己之事。亦或未能深留意也。古之贤臣所以人不足与适。政不足与问。而必以格君心之非为急者。以此也。然则今日缉熙之功。尤不可小缓也。臣等俱以无似。忝在论思之地。以拾遗补阙为职。凡 圣德之有阙失。实臣等之忧。安敢不言。取 进止。
恐自此直言不闻。谀佞成风也。人主一言之得失。人心向背所系。岂可轻哉。 圣教多有未安之语如此。岂平日所望于 圣明者哉。臣等窃恐 殿下格致之功犹或有所未尽。而于诚意正心胜私克己之事。亦或未能深留意也。古之贤臣所以人不足与适。政不足与问。而必以格君心之非为急者。以此也。然则今日缉熙之功。尤不可小缓也。臣等俱以无似。忝在论思之地。以拾遗补阙为职。凡 圣德之有阙失。实臣等之忧。安敢不言。取 进止。成均馆论学政劄
伏以教化。为国之大务也。王者代天理物之道。不但养其民使之安。又当有以教之使之善也。盖风俗非教不善。人材非学不成。古之盛时所以风清俗美。多士济济者。皆由教而致。而孟子论为国之道。以井田与学校并言之。然则学校之教。岂王政之所宜忽哉。我国不幸。自兵变之后。急于治兵。不遑于教。学政遂废。况经废朝昏乱之世。至于田野之间。亦未闻有讲学之人。士风大坏。同然贸贸。几乎人欲肆而天理灭矣。此有识之士所以不胜其忧叹者也。今虽板荡之馀。疮痍未起。教化之道。岂可全然废弛。士习任其坏
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7H 页
 败。风俗任其薄恶。使世道日趋于乱乎。今欲修举教化之道。当推本古昔圣人施教之意以为法。窃考唐虞之际所以为教者。则以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命契为司徒。是契之五教。凡民皆教之也。其命夔曰。教胄子。是夔之四德及诗乐。非教凡民也。只以教胄子也。盖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凡人日用之间。不可须更离者也。故五典之教。施于凡民。至于礼乐学问。则非凡民所能也。故只以教胄子也。三代之教。有大学小学之别。爱亲敬兄忠君悌长之道。小子之学也。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人之学也。大学之道。非小子所能也。故其为教不同也。今欲法古之所以施教之意。则京中四学及外方之士。宜以古人所谓小学之道教之。馆中宜以古人所谓大学之道教之。故臣之愚意。四学及外方学子。宜皆令读小学。馆中。讲近思录,四书,五经等书。小学所缉。皆前古圣贤格言至行。可以为万世法者。使凡为士者反复读之。以为恒业。则必有感发其为善之心者。而风俗亦当少变矣。且篇末。有先儒所论为学之道及读书次第。质美之人。则亦或有因此向意为学者。又不但止为小子之学而已也。至于近思录,四书,五经等书。乃天下
败。风俗任其薄恶。使世道日趋于乱乎。今欲修举教化之道。当推本古昔圣人施教之意以为法。窃考唐虞之际所以为教者。则以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命契为司徒。是契之五教。凡民皆教之也。其命夔曰。教胄子。是夔之四德及诗乐。非教凡民也。只以教胄子也。盖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凡人日用之间。不可须更离者也。故五典之教。施于凡民。至于礼乐学问。则非凡民所能也。故只以教胄子也。三代之教。有大学小学之别。爱亲敬兄忠君悌长之道。小子之学也。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人之学也。大学之道。非小子所能也。故其为教不同也。今欲法古之所以施教之意。则京中四学及外方之士。宜以古人所谓小学之道教之。馆中宜以古人所谓大学之道教之。故臣之愚意。四学及外方学子。宜皆令读小学。馆中。讲近思录,四书,五经等书。小学所缉。皆前古圣贤格言至行。可以为万世法者。使凡为士者反复读之。以为恒业。则必有感发其为善之心者。而风俗亦当少变矣。且篇末。有先儒所论为学之道及读书次第。质美之人。则亦或有因此向意为学者。又不但止为小子之学而已也。至于近思录,四书,五经等书。乃天下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7L 页
 古今义理之府库也。古之圣贤所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皆备于此矣。使学者究心于此。得其意味。则必有慨然奋发者。而此学有兴行之望矣。其节目。谨条陈如后。
古今义理之府库也。古之圣贤所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皆备于此矣。使学者究心于此。得其意味。则必有慨然奋发者。而此学有兴行之望矣。其节目。谨条陈如后。一。京中四学及外方各官士子。皆成册书姓名年岁。一件藏于本学本官。一件送于馆。馆聚京外成册而藏之。每年有新入者。添录于册末。而学则直报于馆。各官则报本道粘移于馆。馆又受而添录于册。新入时皆讲小学。粗以上。许入每榜监试初试。入格者。馆考于册。名无者入 启削去。
一。京外士子年三十五岁以下。皆令读小学。京中则各学官每月初旬会当学。儒生通读小学。在京累月不参者削籍。各官则择境内先辈生进或幼学读书有文理者。令教一邑士子。守令或时考讲。行其赏罚。
一。京中则每季朔。各学官馆官一员会同考讲。录其所讲。粗以上。一件藏于本学。一件藏于馆。外方则春秋考讲。合四五官或五六官定都会。试官以文臣或生进守令。备三员差定。亦录其所讲。粗以上。一件藏于都会官。一件藏于本道。其落讲者。勿遽定军。每式年。通三年所讲。计其画数。每学每道。定其额数。给监
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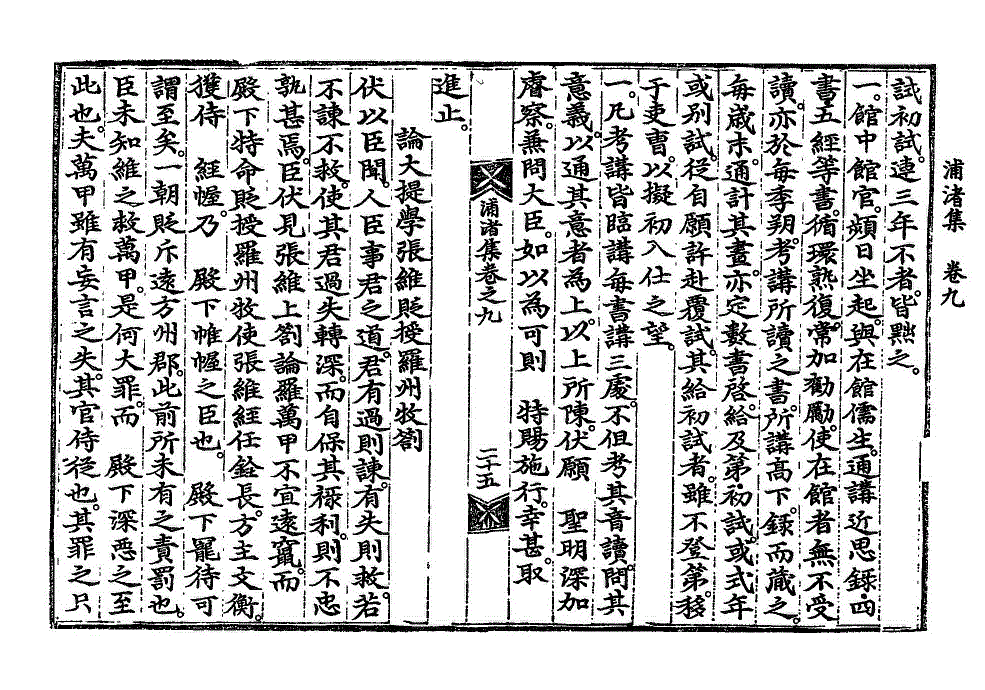 试初试。连三年不者。皆黜之。
试初试。连三年不者。皆黜之。一。馆中馆官。频日坐起。与在馆儒生。通讲近思录,四书,五经等书。循环熟复。常加劝励。使在馆者无不受读。亦于每季朔。考讲所读之书。所讲高下。录而藏之。每岁末。通计其画。亦定数书启。给及第,初试。或式年或别试。从自愿许赴覆试。其给初试者。虽不登第。移于吏曹。以拟初入仕之望。
一。凡考讲皆临讲每书讲三处。不但考其音读。问其意义。以通其意者为上。以上所陈。伏愿 圣明深加睿察。兼问大臣。如以为可则 特赐施行。幸甚。取 进止。
论大提学张维贬授罗州牧劄
伏以臣闻。人臣事君之道。君有过则谏。有失则救。若不谏不救。使其君过失转深。而自保其禄利。则不忠孰甚焉。臣伏见张维上劄论罗万甲不宜远窜。而 殿下特命贬授罗州牧使张维经任铨长。方主文衡。获侍 经幄。乃 殿下帷幄之臣也。 殿下宠待可谓至矣。一朝贬斥远方州郡。此前所未有之责罚也。臣未知维之救万甲。是何大罪。而 殿下深恶之至此也。夫万甲虽有妄言之失。其官侍从也。其罪之只
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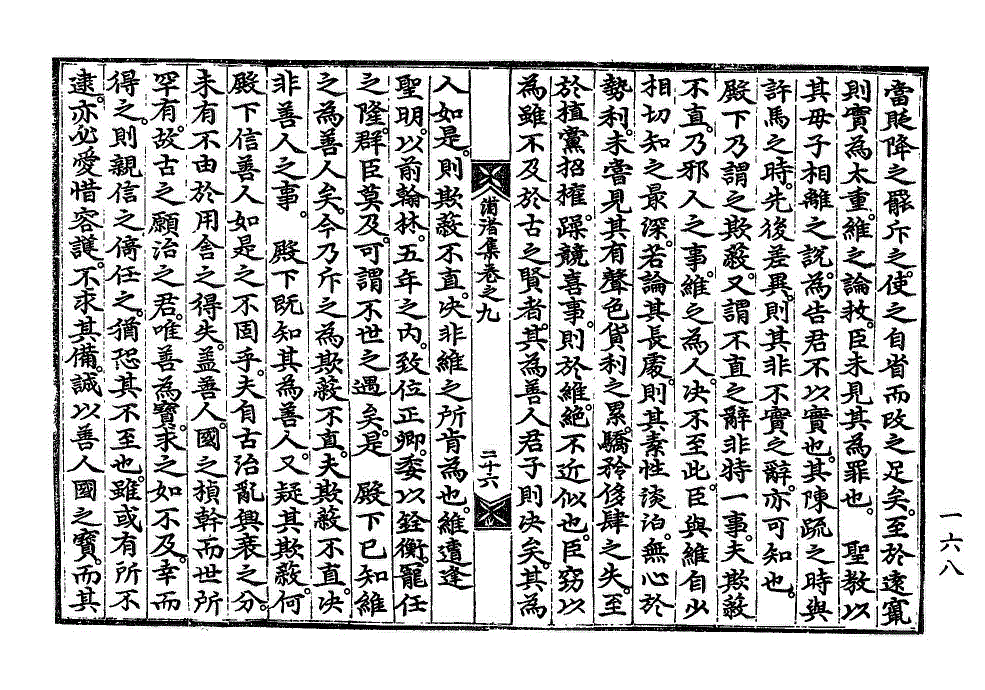 当贬降之罢斥之。使之自省而改之足矣。至于远窜则实为太重。维之论救。臣未见其为罪也。 圣教以其母子相离之说。为告君不以实也。其陈疏之时与许马之时。先后差异。则其非不实之辞。亦可知也。 殿下乃谓之欺蔽。又谓不直之辞非特一事。夫欺蔽不直。乃邪人之事。维之为人。决不至此。臣与维自少相切知之最深。若论其长处。则其素性淡泊。无心于势利。未尝见其有声色货利之累。骄矜侈肆之失。至于植党招权。躁竞喜事。则于维。绝不近似也。臣窃以为虽不及于古之贤者。其为善人君子则决矣。其为人如是。则欺蔽不直。决非维之所肯为也。维遭逢 圣明。以前翰林。五年之内。致位正卿。委以铨衡。宠任之隆。群臣莫及。可谓不世之遇矣。是 殿下已知维之为善人矣。今乃斥之为欺蔽不直。夫欺蔽不直。决非善人之事。 殿下既知其为善人。又疑其欺蔽。何殿下信善人如是之不固乎。夫自古治乱兴衰之分。未有不由于用舍之得失。盖善人。国之桢干而世所罕有。故古之愿治之君。唯善为宝。求之如不及。幸而得之。则亲信之倚任之。犹恐其不至也。虽或有所不逮。亦必爱惜容护。不求其备。诚以善人国之宝。而其
当贬降之罢斥之。使之自省而改之足矣。至于远窜则实为太重。维之论救。臣未见其为罪也。 圣教以其母子相离之说。为告君不以实也。其陈疏之时与许马之时。先后差异。则其非不实之辞。亦可知也。 殿下乃谓之欺蔽。又谓不直之辞非特一事。夫欺蔽不直。乃邪人之事。维之为人。决不至此。臣与维自少相切知之最深。若论其长处。则其素性淡泊。无心于势利。未尝见其有声色货利之累。骄矜侈肆之失。至于植党招权。躁竞喜事。则于维。绝不近似也。臣窃以为虽不及于古之贤者。其为善人君子则决矣。其为人如是。则欺蔽不直。决非维之所肯为也。维遭逢 圣明。以前翰林。五年之内。致位正卿。委以铨衡。宠任之隆。群臣莫及。可谓不世之遇矣。是 殿下已知维之为善人矣。今乃斥之为欺蔽不直。夫欺蔽不直。决非善人之事。 殿下既知其为善人。又疑其欺蔽。何殿下信善人如是之不固乎。夫自古治乱兴衰之分。未有不由于用舍之得失。盖善人。国之桢干而世所罕有。故古之愿治之君。唯善为宝。求之如不及。幸而得之。则亲信之倚任之。犹恐其不至也。虽或有所不逮。亦必爱惜容护。不求其备。诚以善人国之宝。而其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9H 页
 进退为治乱所系也。今 殿下之黜维。可谓用舍之得宜乎。 殿下视今廷臣。文章学识。如维者几人。恬淡寡欲。不失士君子之操行。如维者几人。然则如维者。在于今世。实为难得。 殿下卒然斥逐。曾不顾惜如此。臣窃恐自此善人君子更不为 殿下所惜。自然渐至疏弃。无复存者也。此岂非大可忧者乎。且人君听言之道。当虚心平气。求其理之是非。不可遽以己心之合否为喜怒也。盖己心之所存。未必皆合于至当之理也。故逆于心。必求诸道。逊于志。必求诸非道。虞朝之嘉谟。乐言而莫违。一言可以丧邦。孔子之明戒也。今维 帷幄近臣。当与 殿下争是非可否者也。其言虽或过中。亦当优容。不宜遽加罪斥。今维乃以言获罪。臣窃恐国内之人。皆将谓 殿下乐莫违而怒逆心。虽近臣如维。亦不容也。群臣谁复敢为殿下言者。夫善人斥去。言路杜绝。大非国家之福也。然则维之去。所关岂细乎。罗州。南中大邑。非是恶地。今之朝臣。欲得而不得者亦多矣。以维处之。在维一身。岂必为害。臣之言此。非敢为维惜也。实不免为 圣明忧也。为当世忧也。臣亦尝上劄论万甲事。其罪与维实同。方恐惧屏息。伏俟诛谴。岂合更有所言。第
进退为治乱所系也。今 殿下之黜维。可谓用舍之得宜乎。 殿下视今廷臣。文章学识。如维者几人。恬淡寡欲。不失士君子之操行。如维者几人。然则如维者。在于今世。实为难得。 殿下卒然斥逐。曾不顾惜如此。臣窃恐自此善人君子更不为 殿下所惜。自然渐至疏弃。无复存者也。此岂非大可忧者乎。且人君听言之道。当虚心平气。求其理之是非。不可遽以己心之合否为喜怒也。盖己心之所存。未必皆合于至当之理也。故逆于心。必求诸道。逊于志。必求诸非道。虞朝之嘉谟。乐言而莫违。一言可以丧邦。孔子之明戒也。今维 帷幄近臣。当与 殿下争是非可否者也。其言虽或过中。亦当优容。不宜遽加罪斥。今维乃以言获罪。臣窃恐国内之人。皆将谓 殿下乐莫违而怒逆心。虽近臣如维。亦不容也。群臣谁复敢为殿下言者。夫善人斥去。言路杜绝。大非国家之福也。然则维之去。所关岂细乎。罗州。南中大邑。非是恶地。今之朝臣。欲得而不得者亦多矣。以维处之。在维一身。岂必为害。臣之言此。非敢为维惜也。实不免为 圣明忧也。为当世忧也。臣亦尝上劄论万甲事。其罪与维实同。方恐惧屏息。伏俟诛谴。岂合更有所言。第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69L 页
 见维之去。所关如此。臣猥蒙 天宠。致身宰列。叨窃显要。前后非一。 恩遇之重。非凡臣之比。何敢畏其获罪。而不为一言。自陷于不忠哉。伏愿 圣明矜其愚而察其忱。不胜幸甚。取 进止。
见维之去。所关如此。臣猥蒙 天宠。致身宰列。叨窃显要。前后非一。 恩遇之重。非凡臣之比。何敢畏其获罪。而不为一言。自陷于不忠哉。伏愿 圣明矜其愚而察其忱。不胜幸甚。取 进止。因雷变言事劄(庚午○副提学时)
伏以臣等伏见 圣教。以 太庙树木雷震之变。令中外臣民各陈所怀。窃以春月才半。稚阳用事。雷始发声。未宜震击。而所震不于他处。乃于 太庙垣墙之内。臣等闻见所及。曾所未有。窃以为此莫大之变也。此固变异之最可惊可惧者。而近年以来。凡变异之见。殆不可胜言。水旱连年。饥馑荐臻。以致公私贫乏俱极。而至于日月星文虹蜺氛气。种种灾异。殆至于每月每日而见。柰何 圣明图治之日。众异俱见。频数稠叠如此也。臣等窃闻人事有失。天示之变。又闻变不虚生。必有其应。以今兹变异之大且众观之。则其应必有不可胜忧者。而其所以致此之由。则人事必大有所失以致之。非一二少失所致也。其应之之道。必大震惧大警省。凡政令事为不合于天意。可以召致灾沴者。一切改革。乃为应天以实。而庶几可以消弭也。非小小文具所可塞也。致变之由。臣等固
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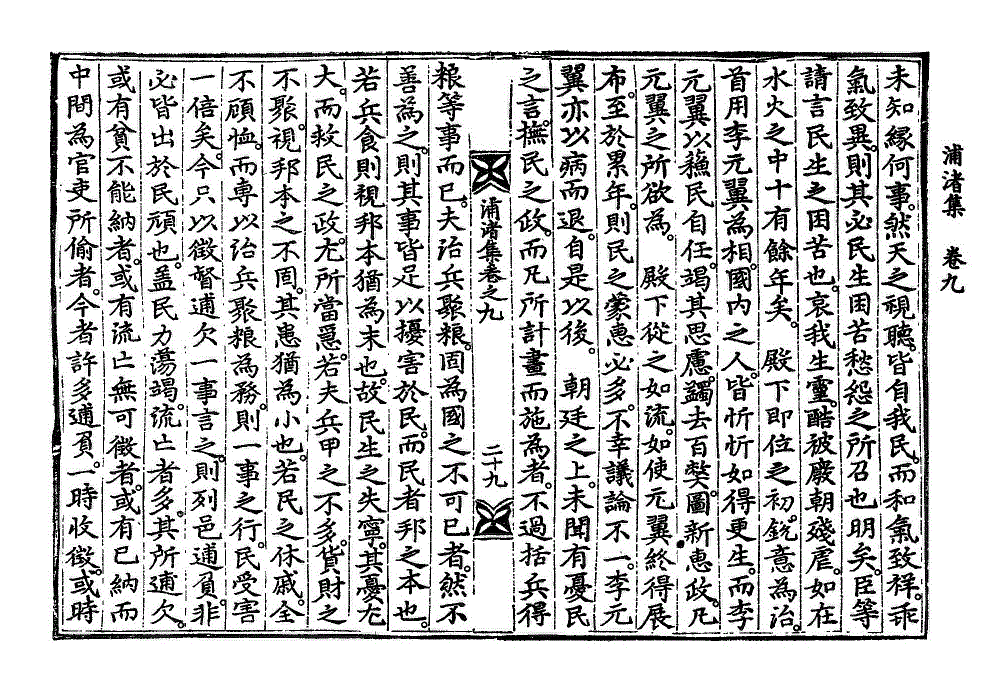 未知缘何事。然天之视听。皆自我民。而和气致祥。乖气致异。则其必民生困苦愁怨之所召也明矣。臣等请言民生之困苦也。哀我生灵。酷被废朝残虐。如在水火之中十有馀年矣。 殿下即位之初。锐意为治。首用李元翼为相。国内之人。皆忻忻如得更生。而李元翼以苏民自任。竭其思虑。蠲去百弊。图新惠政。凡元翼之所欲为。 殿下从之如流。如使元翼。终得展布。至于累年。则民之蒙惠必多。不幸议论不一。李元翼亦以病而退。自是以后。 朝廷之上。未闻有忧民之言。抚民之政。而凡所计画而施为者。不过括兵得粮等事而已。夫治兵聚粮。固为国之不可已者。然不善为之。则其事皆足以扰害于民。而民者邦之本也。若兵食则视邦本犹为末也。故民生之失宁。其忧尤大。而救民之政。尤所当急。若夫兵甲之不多。货财之不聚。视邦本之不固。其患犹为小也。若民之休戚。全不顾恤。而专以治兵聚粮为务。则一事之行。民受害一倍矣。今只以徵督逋欠一事言之。则列邑逋负。非必皆出于民顽也。盖民力荡竭。流亡者多。其所逋欠。或有贫不能纳者。或有流亡无可徵者。或有已纳而中间为官吏所偷者。今者许多逋负。一时收徵。或时
未知缘何事。然天之视听。皆自我民。而和气致祥。乖气致异。则其必民生困苦愁怨之所召也明矣。臣等请言民生之困苦也。哀我生灵。酷被废朝残虐。如在水火之中十有馀年矣。 殿下即位之初。锐意为治。首用李元翼为相。国内之人。皆忻忻如得更生。而李元翼以苏民自任。竭其思虑。蠲去百弊。图新惠政。凡元翼之所欲为。 殿下从之如流。如使元翼。终得展布。至于累年。则民之蒙惠必多。不幸议论不一。李元翼亦以病而退。自是以后。 朝廷之上。未闻有忧民之言。抚民之政。而凡所计画而施为者。不过括兵得粮等事而已。夫治兵聚粮。固为国之不可已者。然不善为之。则其事皆足以扰害于民。而民者邦之本也。若兵食则视邦本犹为末也。故民生之失宁。其忧尤大。而救民之政。尤所当急。若夫兵甲之不多。货财之不聚。视邦本之不固。其患犹为小也。若民之休戚。全不顾恤。而专以治兵聚粮为务。则一事之行。民受害一倍矣。今只以徵督逋欠一事言之。则列邑逋负。非必皆出于民顽也。盖民力荡竭。流亡者多。其所逋欠。或有贫不能纳者。或有流亡无可徵者。或有已纳而中间为官吏所偷者。今者许多逋负。一时收徵。或时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0L 页
 存者为流亡之役。或已纳者有叠徵之患。而以贫残穷民之力。应积年之欠。其势有所不给。守令之未能充补。其出于要誉者。固或有之。其诚心爱民。而势不得捧者亦必有之。今乃一切绳之以要誉之罪。窃恐自此为官吏者。无复敢施宽惠。而竞为刻急。民益不堪也。十数年来涂炭困悴之民。财力已尽。命脉仅存。如人大病之馀气力未苏。羸弱已甚。而加以师旅饥馑。反覆相因。未有宁息之时。今者抚恤之政未见行之。而侵扰之事不一其端。然则吾民安得而不困苦。安得而不愁怨也。天人感召。影响不差。民之怨苦如是。则天心何自而悦豫。变异之作。实乖气之所致也。以近日都民之事观之。则都中应役之民。唯市井而已。市井之人。屡经奔窜。又连值凶歉。其财货之积。商贩之利。岂能如前日。而唐胡差贸易之侵。所失辄至数千之银。此市民所以重困也。而近日 丰呈所用各样器物及尚方仪物之造。别宫修理之事。并出于一时。而皆用市民之力。以都中数十各市之民。应许多一时并出之役。每市所出。其数不赀。市民男女。搥胸叩心。流涕呼泣之状。不可忍见。然则京外之民。怨苦同然也。 殿下居深宫之中。群臣亦未有以此上
存者为流亡之役。或已纳者有叠徵之患。而以贫残穷民之力。应积年之欠。其势有所不给。守令之未能充补。其出于要誉者。固或有之。其诚心爱民。而势不得捧者亦必有之。今乃一切绳之以要誉之罪。窃恐自此为官吏者。无复敢施宽惠。而竞为刻急。民益不堪也。十数年来涂炭困悴之民。财力已尽。命脉仅存。如人大病之馀气力未苏。羸弱已甚。而加以师旅饥馑。反覆相因。未有宁息之时。今者抚恤之政未见行之。而侵扰之事不一其端。然则吾民安得而不困苦。安得而不愁怨也。天人感召。影响不差。民之怨苦如是。则天心何自而悦豫。变异之作。实乖气之所致也。以近日都民之事观之。则都中应役之民。唯市井而已。市井之人。屡经奔窜。又连值凶歉。其财货之积。商贩之利。岂能如前日。而唐胡差贸易之侵。所失辄至数千之银。此市民所以重困也。而近日 丰呈所用各样器物及尚方仪物之造。别宫修理之事。并出于一时。而皆用市民之力。以都中数十各市之民。应许多一时并出之役。每市所出。其数不赀。市民男女。搥胸叩心。流涕呼泣之状。不可忍见。然则京外之民。怨苦同然也。 殿下居深宫之中。群臣亦未有以此上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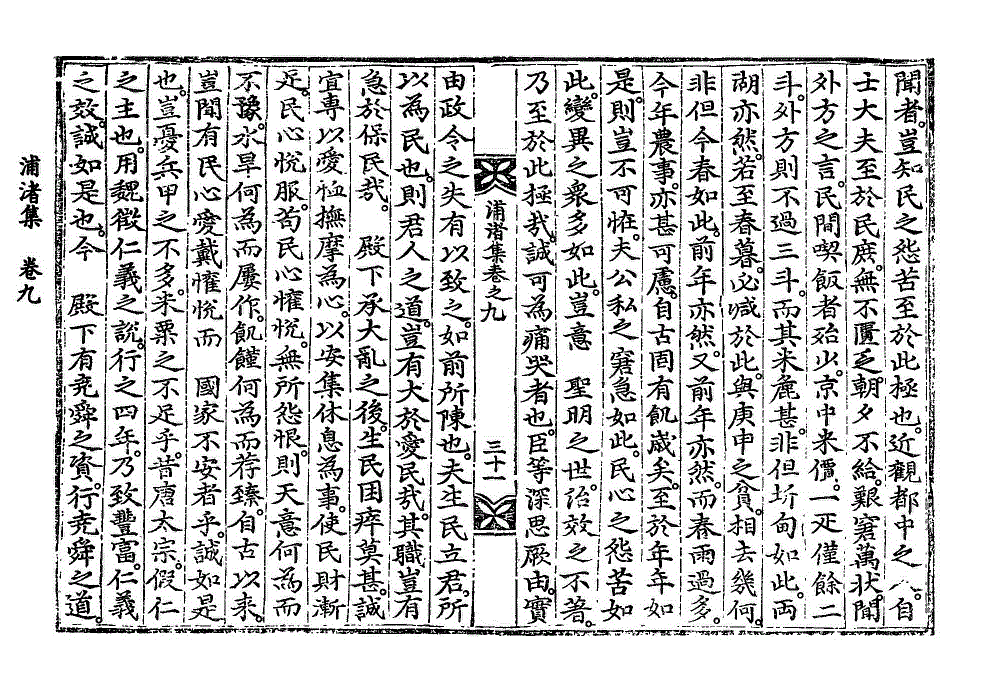 闻者。岂知民之怨苦至于此极也。近观都中之人。自士大夫至于民庶。无不匮乏。朝夕不给。艰窘万状。闻外方之言。民间吃饭者殆少。京中米价。一疋仅馀二斗。外方则不过三斗。而其米粗甚。非但圻甸如此。两湖亦然。若至春暮。必减于此。与庚申之贫。相去几何。非但今春如此。前年亦然。又前年亦然。而春雨过多。今年农事。亦甚可虑。自古固有饥岁矣。至于年年如是。则岂不可怪。夫公私之窘急如此。民心之怨苦如此。变异之众多如此。岂意 圣明之世。治效之不著。乃至于此极哉。诚可为痛哭者也。臣等深思厥由。实由政令之失有以致之。如前所陈也。夫生民立君。所以为民也。则君人之道。岂有大于爱民哉。其职岂有急于保民哉。 殿下承大乱之后。生民困瘁莫甚。诚宜专以爱恤抚摩为心。以安集休息为事。使民财渐足。民心悦服。苟民心欢悦。无所怨恨。则天意何为而不豫。水旱何为而屡作。饥馑何为而荐臻。自古以来。岂闻有民心爱戴欢悦而 国家不安者乎。诚如是也。岂忧兵甲之不多。米粟之不足乎。昔唐太宗。假仁之主也。用魏徵仁义之说。行之四年。乃致丰富。仁义之效。诚如是也。今 殿下有尧舜之资。行尧舜之道。
闻者。岂知民之怨苦至于此极也。近观都中之人。自士大夫至于民庶。无不匮乏。朝夕不给。艰窘万状。闻外方之言。民间吃饭者殆少。京中米价。一疋仅馀二斗。外方则不过三斗。而其米粗甚。非但圻甸如此。两湖亦然。若至春暮。必减于此。与庚申之贫。相去几何。非但今春如此。前年亦然。又前年亦然。而春雨过多。今年农事。亦甚可虑。自古固有饥岁矣。至于年年如是。则岂不可怪。夫公私之窘急如此。民心之怨苦如此。变异之众多如此。岂意 圣明之世。治效之不著。乃至于此极哉。诚可为痛哭者也。臣等深思厥由。实由政令之失有以致之。如前所陈也。夫生民立君。所以为民也。则君人之道。岂有大于爱民哉。其职岂有急于保民哉。 殿下承大乱之后。生民困瘁莫甚。诚宜专以爱恤抚摩为心。以安集休息为事。使民财渐足。民心悦服。苟民心欢悦。无所怨恨。则天意何为而不豫。水旱何为而屡作。饥馑何为而荐臻。自古以来。岂闻有民心爱戴欢悦而 国家不安者乎。诚如是也。岂忧兵甲之不多。米粟之不足乎。昔唐太宗。假仁之主也。用魏徵仁义之说。行之四年。乃致丰富。仁义之效。诚如是也。今 殿下有尧舜之资。行尧舜之道。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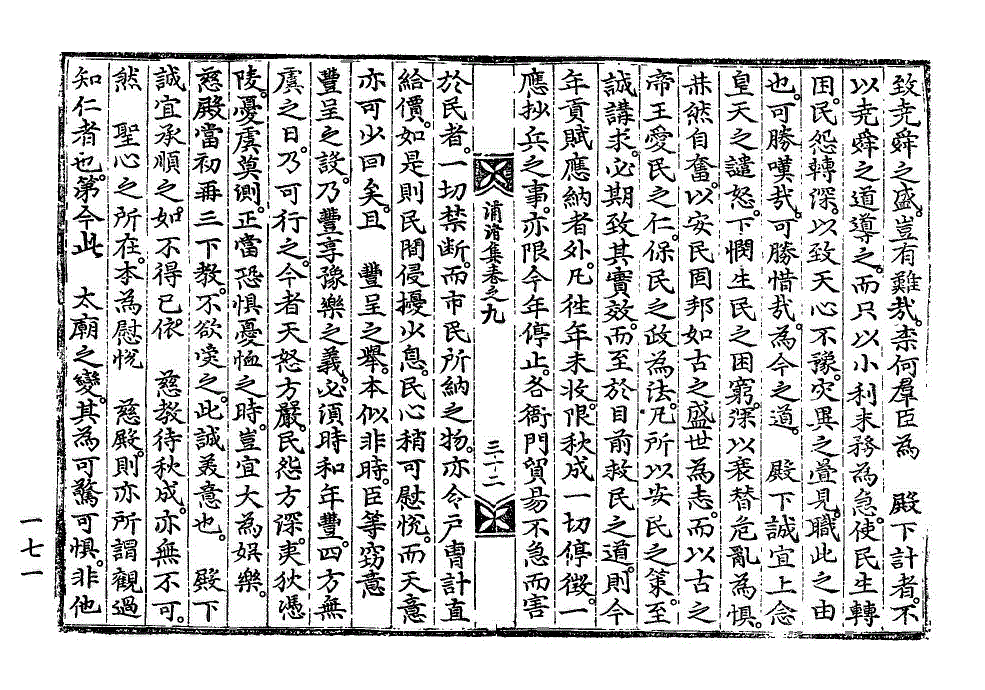 致尧舜之盛。岂有难哉。柰何群臣为 殿下计者。不以尧舜之道导之。而只以小利末务为急。使民生转困。民怨转深。以致天心不豫。灾异之叠见。职此之由也。可胜叹哉。可胜惜哉。为今之道。 殿下诚宜上念皇天之谴怒。下悯生民之困穷。深以衰替危乱为惧。赫然自奋。以安民固邦如古之盛世为志。而以古之帝王爱民之仁。保民之政为法。凡所以安民之策。至诚讲求。必期致其实效。而至于目前救民之道。则今年贡赋应纳者外。凡往年未收。限秋成一切停徵。一应抄兵之事。亦限今年停止。各衙门贸易不急而害于民者。一切禁断。而市民所纳之物。亦令户曹计直给价。如是则民间侵扰少息。民心稍可慰悦。而天意亦可少回矣。且 丰呈之举。本似非时。臣等窃意 丰呈之设。乃丰享(一作亨)豫乐之义。必须时和年丰。四方无虞之日。乃可行之。今者天怒方严。民怨方深。夷狄凭陵。忧虞莫测。正当恐惧忧恤之时。岂宜大为娱乐。 慈殿当初再三下教。不欲受之。此诚美意也。 殿下诚宜承顺之。如不得已。依 慈教待秋成。亦无不可。然 圣心之所在。本为慰悦 慈殿。则亦所谓观过知仁者也。第今此 太庙之变。其为可惊可惧。非他
致尧舜之盛。岂有难哉。柰何群臣为 殿下计者。不以尧舜之道导之。而只以小利末务为急。使民生转困。民怨转深。以致天心不豫。灾异之叠见。职此之由也。可胜叹哉。可胜惜哉。为今之道。 殿下诚宜上念皇天之谴怒。下悯生民之困穷。深以衰替危乱为惧。赫然自奋。以安民固邦如古之盛世为志。而以古之帝王爱民之仁。保民之政为法。凡所以安民之策。至诚讲求。必期致其实效。而至于目前救民之道。则今年贡赋应纳者外。凡往年未收。限秋成一切停徵。一应抄兵之事。亦限今年停止。各衙门贸易不急而害于民者。一切禁断。而市民所纳之物。亦令户曹计直给价。如是则民间侵扰少息。民心稍可慰悦。而天意亦可少回矣。且 丰呈之举。本似非时。臣等窃意 丰呈之设。乃丰享(一作亨)豫乐之义。必须时和年丰。四方无虞之日。乃可行之。今者天怒方严。民怨方深。夷狄凭陵。忧虞莫测。正当恐惧忧恤之时。岂宜大为娱乐。 慈殿当初再三下教。不欲受之。此诚美意也。 殿下诚宜承顺之。如不得已。依 慈教待秋成。亦无不可。然 圣心之所在。本为慰悦 慈殿。则亦所谓观过知仁者也。第今此 太庙之变。其为可惊可惧。非他浦渚先生集卷之九 第 1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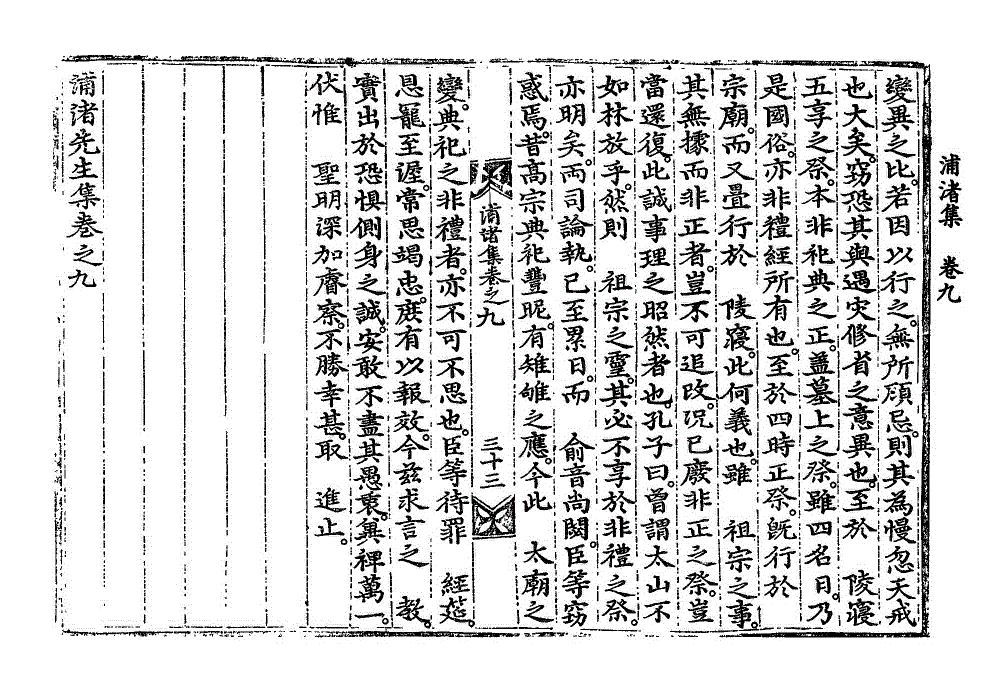 变异之比。若因以行之。无所顾忌。则其为慢忽天戒也大矣。窃恐其与遇灾修省之意异也。至于 陵寝五享之祭。本非祀典之正。盖墓上之祭。虽四名日。乃是国俗。亦非礼经所有也。至于四时正祭。既行于 宗庙。而又叠行于 陵寝。此何义也。虽 祖宗之事。其无据而非正者。岂不可追改。况已废非正之祭。岂当还复。此诚事理之昭然者也。孔子曰。曾谓太山不如林放乎。然则 祖宗之灵。其必不享于非礼之祭。亦明矣。两司论执。已至累日。而 俞音尚閟。臣等窃惑焉。昔高宗典祀丰昵。有雉雊之应。今此 太庙之变。典祀之非礼者。亦不可不思也。臣等待罪 经筵。恩宠至渥。常思竭忠。庶有以报效。今兹求言之 教。实出于恐惧侧身之诚。安敢不尽其愚衷。冀裨万一。伏惟 圣明深加睿察。不胜幸甚。取 进止。
变异之比。若因以行之。无所顾忌。则其为慢忽天戒也大矣。窃恐其与遇灾修省之意异也。至于 陵寝五享之祭。本非祀典之正。盖墓上之祭。虽四名日。乃是国俗。亦非礼经所有也。至于四时正祭。既行于 宗庙。而又叠行于 陵寝。此何义也。虽 祖宗之事。其无据而非正者。岂不可追改。况已废非正之祭。岂当还复。此诚事理之昭然者也。孔子曰。曾谓太山不如林放乎。然则 祖宗之灵。其必不享于非礼之祭。亦明矣。两司论执。已至累日。而 俞音尚閟。臣等窃惑焉。昔高宗典祀丰昵。有雉雊之应。今此 太庙之变。典祀之非礼者。亦不可不思也。臣等待罪 经筵。恩宠至渥。常思竭忠。庶有以报效。今兹求言之 教。实出于恐惧侧身之诚。安敢不尽其愚衷。冀裨万一。伏惟 圣明深加睿察。不胜幸甚。取 进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