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x 页
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疏(十四首)
疏(十四首)
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03H 页
 辞右议政疏(己丑)
辞右议政疏(己丑)伏以臣赋性愚朴鄙拙。才能无可取。百事不能及人。少占科第。以愚拙之故。不得见取于人。沈于下流者有年。中间虽少通清路。而旋即颠踬。自分永弃。及 反正之后。遭逢 圣主之知。累忝非分之职。以至致位卿秩。盖自癸亥至丙子。其在 朝从宦。凡十有四年。自丁丑以后。又流落乡曲。初因罪废。及蒙 牧叙。又以亲老。乞养退伏。获罪于天。终至祸故。盖自释褐至前年。凡四十有七年。而其间实历。不能三分之一矣。岁月如流。衰老忽及。今年七十有一矣。七十致仕。古人定制。况臣衰门多衅。七八年间。惨祸连仍。长以悲伤摧割度日。其精神之昏瞀。气力之消耗。不比他人七十者。前岁趋 召上来。自顾衰朽。馀日无多。惟思终老田野。实无一毫世念。伏蒙 先王怜恤旧物。不忍捐弃。三疏乞骸。 圣批勤恳。不许退归。臣窃感激。不敢更言去。窃计年岁之间。且留都下。待衰齿又加一年。可更乞退。不意皇天降割。遽遭 宾天之痛。区区哀慕之情。曷有其极。而寻常一念。长在草野。行
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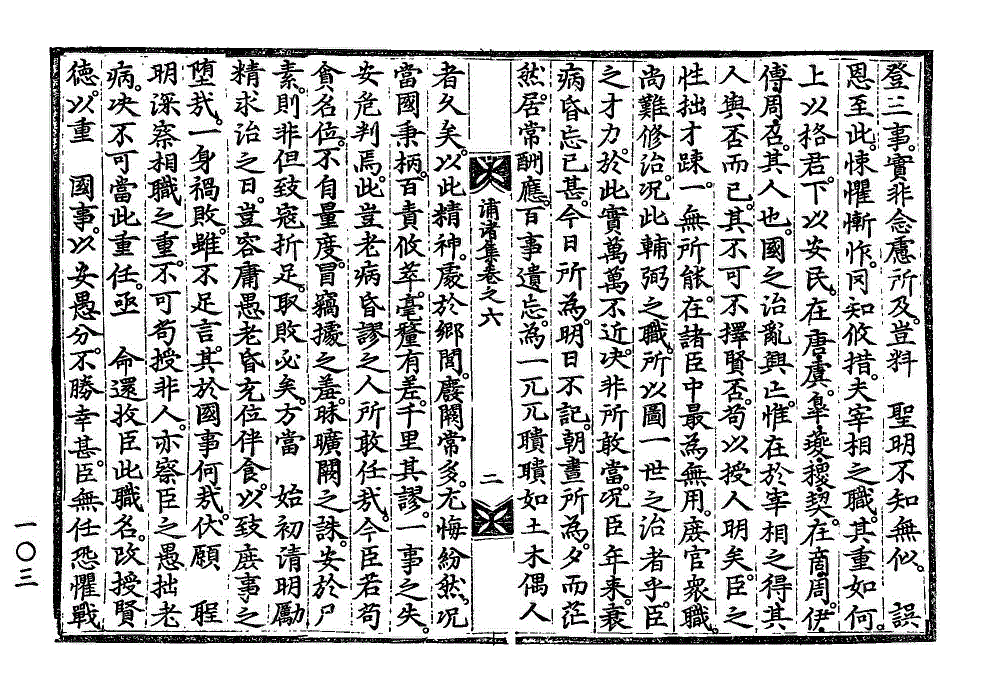 登三事。实非念虑所及。岂料 圣明不知无似。 误恩至此。悚惧惭怍。罔知攸措。夫宰相之职。其重如何。上以格君。下以安民。在唐,虞。皋,夔,稷,契。在商,周。伊,傅,周,召。其人也。国之治乱兴亡。惟在于宰相之得其人与否而已。其不可不择贤否。苟以授人明矣。臣之性拙才疏。一无所能。在诸臣中最为无用。庶官众职。尚难修治。况此辅弼之职。所以图一世之治者乎。臣之才力。于此实万万不近。决非所敢当。况臣年来。衰病昏忘已甚。今日所为。明日不记。朝昼所为。夕而茫然。居常酬应。百事遗忘。为一兀兀聩聩如土木偶人者久矣。以此精神。处于乡闾。废阙常多。尤悔纷然。况当国秉柄。百责攸萃。毫釐有差。千里其谬。一事之失。安危判焉。此岂老病昏谬之人所敢任哉。今臣若苟贪名位。不自量度。冒窃据之羞。昧旷阙之诛。安于尸素。则非但致寇折足。取败必矣。方当 始初清明励精求治之日。岂容庸愚老昏充位伴食。以致庶事之堕哉。一身祸败。虽不足言。其于国事何哉。伏愿 圣明深察相职之重。不可苟授非人。亦察臣之愚拙老病。决不可当此重任。亟 命还收臣此职名。改授贤德。以重 国事。以安愚分。不胜幸甚。臣无任恐惧战
登三事。实非念虑所及。岂料 圣明不知无似。 误恩至此。悚惧惭怍。罔知攸措。夫宰相之职。其重如何。上以格君。下以安民。在唐,虞。皋,夔,稷,契。在商,周。伊,傅,周,召。其人也。国之治乱兴亡。惟在于宰相之得其人与否而已。其不可不择贤否。苟以授人明矣。臣之性拙才疏。一无所能。在诸臣中最为无用。庶官众职。尚难修治。况此辅弼之职。所以图一世之治者乎。臣之才力。于此实万万不近。决非所敢当。况臣年来。衰病昏忘已甚。今日所为。明日不记。朝昼所为。夕而茫然。居常酬应。百事遗忘。为一兀兀聩聩如土木偶人者久矣。以此精神。处于乡闾。废阙常多。尤悔纷然。况当国秉柄。百责攸萃。毫釐有差。千里其谬。一事之失。安危判焉。此岂老病昏谬之人所敢任哉。今臣若苟贪名位。不自量度。冒窃据之羞。昧旷阙之诛。安于尸素。则非但致寇折足。取败必矣。方当 始初清明励精求治之日。岂容庸愚老昏充位伴食。以致庶事之堕哉。一身祸败。虽不足言。其于国事何哉。伏愿 圣明深察相职之重。不可苟授非人。亦察臣之愚拙老病。决不可当此重任。亟 命还收臣此职名。改授贤德。以重 国事。以安愚分。不胜幸甚。臣无任恐惧战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04H 页
 灼激切祈恳之至。谨昧死以 闻。
灼激切祈恳之至。谨昧死以 闻。辞右议政疏[再疏]
伏以 殿下以圣哲之资。嗣艰大之业。闷邦家之不理。惧时事之多虞。思欲振举颓废。期致盛治。择辅相之人。而乃及于臣。臣实庸愚。决不可堪任此职。窃不胜惊惶闷惧。冒陈其不可堪之实。以冀镌免。伏承 圣批。乃谓臣才学德行。允合辅弼之职。又曰。速出论道。以济时艰。臣于是乃伏审 殿下误以臣为贤。拔而置诸爰立之位。而责之以经济之事业也。臣尤窃悚惧闷蹙。罔知攸措。 殿下虽不知臣之不肖。误以为贤。而授之以不可堪之任。臣则自知不肖甚明。安敢自诬为贤以欺 殿下。而滥受不可堪之任。以坏殿下知人之明。而以自纳于不测之罪哉。 圣教所谓才学德行四字。于臣绝不近似。语其才则天赋本自鲁钝。百不及人。至于德行。尤蔑蔑无有。惟学则尝窃少用其力。而以鲁钝之故。徒弊时月。实无所得。迂愚固滞。甚于不学之人。其有何可取之实哉。声闻过情。古人所耻。况 圣明之知。皆非其实。其为愧怍震恐。何地自容。况臣年纪已至晚暮。气力之消耗。精神之昏谬。乃理所固然。而积年悲伤。丧魂失魄。百事茫
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04L 页
 然。又常多疾病。盖缘根本已伤。少或失摄辄累日作痛。或至旬月不差。比比而然。其才力本无可取。而老病又如此。其不可当重任决矣。况今国势陵夷。纪纲大坏。百弊俱兴。朝论乖离。万目睽睽。民生失宁。怨苦嗷嗷。当此之时。须得出类之贤杰。改纪振作。大施功力。庶几正人心而整纪纲。革弊政而苏民生。治道有可望矣。岂可使凡庸之人循序苟充而已哉。况臣之愚拙老病。于此万不近似。此臣所以冒陈哀恳。缕缕之至此。而不自知止者也。伏愿 圣明深察此职非凡庸所可冒据。舍臣庸愚老病百不可用之人。而极其搜访。必得当世贤才可堪此任者而授之。则岂但愚臣是幸。实 国家之大幸也。臣无任瞻天望 圣恳祈屏营之至。谨昧死以 闻。
然。又常多疾病。盖缘根本已伤。少或失摄辄累日作痛。或至旬月不差。比比而然。其才力本无可取。而老病又如此。其不可当重任决矣。况今国势陵夷。纪纲大坏。百弊俱兴。朝论乖离。万目睽睽。民生失宁。怨苦嗷嗷。当此之时。须得出类之贤杰。改纪振作。大施功力。庶几正人心而整纪纲。革弊政而苏民生。治道有可望矣。岂可使凡庸之人循序苟充而已哉。况臣之愚拙老病。于此万不近似。此臣所以冒陈哀恳。缕缕之至此。而不自知止者也。伏愿 圣明深察此职非凡庸所可冒据。舍臣庸愚老病百不可用之人。而极其搜访。必得当世贤才可堪此任者而授之。则岂但愚臣是幸。实 国家之大幸也。臣无任瞻天望 圣恳祈屏营之至。谨昧死以 闻。辞右议政疏[三疏]
伏以臣上章乞免至于再矣。而 殿下不加谅察。不即 允许。臣之两疏。非是虚让。实出于恐惧闷迫之情也。夫宰相之职。非一官一职之比。一国之事。无所不当知。凡君德之修否。庶政之得失。生民之休戚。无不系于宰相。此其可易而当之哉。且 殿下所以择于诸臣之中。而授之以此任者。岂使之备员而已哉。
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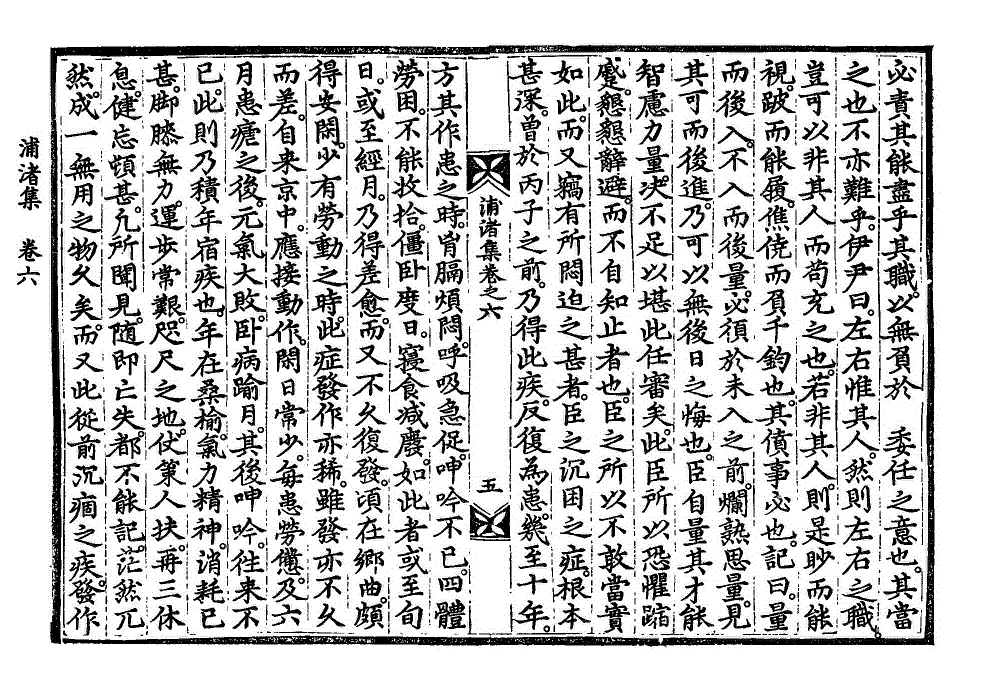 必责其能尽乎其职。以无负于 委任之意也。其当之也不亦难乎。伊尹曰。左右惟其人。然则左右之职。岂可以非其人而苟充之也。若非其人。则是眇而能视。跛而能履。僬侥而负千钧也。其偾事必也。记曰。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必须于未入之前。烂熟思量。见其可而后进。乃可以无后日之悔也。臣自量其才能智虑力量。决不足以堪此任审矣。此臣所以恐惧蹜蹙。恳恳辞避。而不自知止者也。臣之所以不敢当实如此。而又窃有所闷迫之甚者。臣之沈困之症。根本甚深。曾于丙子之前。乃得此疾。反复为患。几至十年。方其作患之时。胸膈烦闷。呼吸急促。呻吟不已。四体劳困。不能收拾。僵卧度日。寝食减废。如此者或至旬日。或至经月。乃得差愈。而又不久复发。顷在乡曲。颇得安闲。少有劳动之时。此症发作亦稀。虽发亦不久而差。自来京中。应接动作。闲日常少。每患劳惫。及六月患疟之后。元气大败。卧病踰月。其后呻吟。往来不已。此则乃积年宿疾也。年在桑榆。气力精神。消耗已甚。脚膝无力。运步常艰。咫尺之地。仗策人扶。再三休息。健忘顿甚。凡所闻见。随即亡失。都不能记。茫然兀然。成一无用之物久矣。而又此从前沈痼之疾。发作
必责其能尽乎其职。以无负于 委任之意也。其当之也不亦难乎。伊尹曰。左右惟其人。然则左右之职。岂可以非其人而苟充之也。若非其人。则是眇而能视。跛而能履。僬侥而负千钧也。其偾事必也。记曰。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必须于未入之前。烂熟思量。见其可而后进。乃可以无后日之悔也。臣自量其才能智虑力量。决不足以堪此任审矣。此臣所以恐惧蹜蹙。恳恳辞避。而不自知止者也。臣之所以不敢当实如此。而又窃有所闷迫之甚者。臣之沈困之症。根本甚深。曾于丙子之前。乃得此疾。反复为患。几至十年。方其作患之时。胸膈烦闷。呼吸急促。呻吟不已。四体劳困。不能收拾。僵卧度日。寝食减废。如此者或至旬日。或至经月。乃得差愈。而又不久复发。顷在乡曲。颇得安闲。少有劳动之时。此症发作亦稀。虽发亦不久而差。自来京中。应接动作。闲日常少。每患劳惫。及六月患疟之后。元气大败。卧病踰月。其后呻吟。往来不已。此则乃积年宿疾也。年在桑榆。气力精神。消耗已甚。脚膝无力。运步常艰。咫尺之地。仗策人扶。再三休息。健忘顿甚。凡所闻见。随即亡失。都不能记。茫然兀然。成一无用之物久矣。而又此从前沈痼之疾。发作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05L 页
 为患。自顾才力本不堪当此重任。而老病又如此。其瘝旷决矣。一身罪戾。虽不足言。相职旷阙。岂不为国之大患。此臣之所大惧也。伏愿 圣明察臣才力之无可取。怜臣老病之不可用。亟 命还收新授之重任。更求贤才而授之。则 国事幸甚。愚臣幸甚。
为患。自顾才力本不堪当此重任。而老病又如此。其瘝旷决矣。一身罪戾。虽不足言。相职旷阙。岂不为国之大患。此臣之所大惧也。伏愿 圣明察臣才力之无可取。怜臣老病之不可用。亟 命还收新授之重任。更求贤才而授之。则 国事幸甚。愚臣幸甚。论俞棨等事疏
伏以臣昨者入侍。妄论俞棨事。以致 天怒赫然。至下俞棨,沈大孚窜谪之 命。臣震恐缩伏。措躬无所。直欲钻地以入也。第窃念 君臣之间。贵在情意相通。兹敢冒死仰渎焉。凡人君临下听言之道。惟当平心察之。求其意之所在。则其有罪无罪有情无情。皆可以照见矣。夫 先王仁圣之德。举国所共感戴。人臣岂敢有讥贬之者。虽病风丧心之人。必不敢如是也。以是窃恐棨之论。只以 谥号叠用为疑耳。岂见有他意也。臣非独深蒙 先王恩宠。实深感 先王仁厚之德。寻常与人言论。未尝不钦叹不已。实所谓贤贤亲亲。没世不忘者也。若使棨有一毫不足于 先王之心。臣亦当痛疾之矣。且臣虽至庸极陋。无所比数。犹窃有区区好善疾恶之心。而赋性偏狭。未能苟同。如见有讥谤 先王之人。则岂不为之深恶。而
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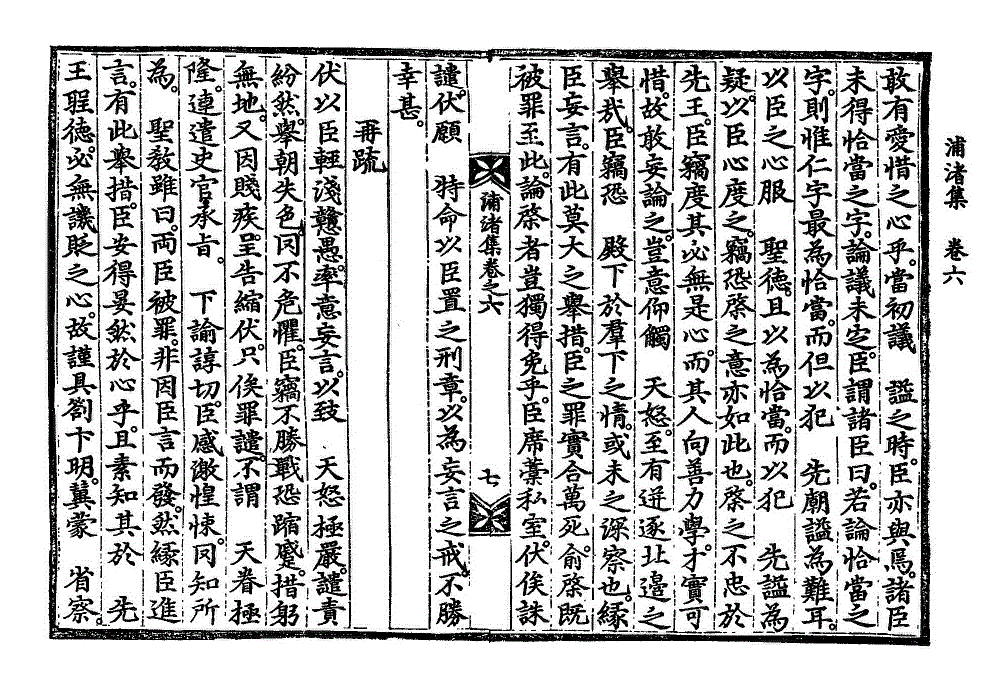 敢有爱惜之心乎。当初议 谥之时。臣亦与焉。诸臣未得恰当之字。论议未定。臣谓诸臣曰。若论恰当之字。则惟仁字最为恰当。而但以犯 先庙谥为难耳。以臣之心服 圣德。且以为恰当。而以犯 先谥为疑。以臣心度之。窃恐棨之意亦如此也。棨之不忠于先王。臣窃度其必无是心。而其人向善力学。才实可惜。故敢妄论之。岂意仰触 天怒。至有迸逐北边之举哉。臣窃恐 殿下于群下之情。或未之深察也。缘臣妄言。有此莫大之举措。臣之罪实合万死。俞棨既被罪至此。论棨者岂独得免乎。臣席藁私室。伏俟诛谴。伏愿 特命以臣置之刑章。以为妄言之戒。不胜幸甚。
敢有爱惜之心乎。当初议 谥之时。臣亦与焉。诸臣未得恰当之字。论议未定。臣谓诸臣曰。若论恰当之字。则惟仁字最为恰当。而但以犯 先庙谥为难耳。以臣之心服 圣德。且以为恰当。而以犯 先谥为疑。以臣心度之。窃恐棨之意亦如此也。棨之不忠于先王。臣窃度其必无是心。而其人向善力学。才实可惜。故敢妄论之。岂意仰触 天怒。至有迸逐北边之举哉。臣窃恐 殿下于群下之情。或未之深察也。缘臣妄言。有此莫大之举措。臣之罪实合万死。俞棨既被罪至此。论棨者岂独得免乎。臣席藁私室。伏俟诛谴。伏愿 特命以臣置之刑章。以为妄言之戒。不胜幸甚。论俞棨等事疏[再疏]
伏以臣轻浅戆愚。率意妄言。以致 天怒极严。谴责纷然。举朝失色。罔不危惧。臣窃不胜战恐蹜蹙。措躬无地。又因贱疾。呈告缩伏。只俟罪谴。不谓 天眷极隆。连遣史官,承旨。 下谕谆切。臣感激惶悚。罔知所为。 圣教虽曰。两臣被罪。非因臣言而发。然缘臣进言。有此举措。臣安得晏然于心乎。且素知其于 先王圣德。必无讥贬之心。故谨具劄卞明。冀蒙 省察。
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06L 页
 未及上进。伏见昨暮赵锡胤 批答之辞。乃伏审 圣心深怒棨等。蕴蓄已久。乃发于今日也。夫 圣意既以棨等为贬薄 先王。则其怒之也。乃怒所当怒也。于此益见 圣孝之至。窃不胜感激叹服之深也。而其言心中所蕴。罄尽如此。此诚所谓开心见诚。无所隐伏者。 君臣之间。相与罄尽如是。则岂复有疑间之存于其中哉。此尤帝王之盛节。尤不任叹服之至也。夫 殿下既罄尽如是。臣安敢不悉陈其心之所疑乎。 圣教谓棨再上疏章。初则辞意不至已甚。其再则敢举 庙号而斥言之。臣窃闻棨只为一疏。不为再疏。考之政院日记。亦然云。然则其再疏所言。必非棨所为也。臣窃恐 殿下于创巨之初。荒迷之际。见他人疏而认为棨疏也。臣敢疑 殿下荒迷之中有所不察。罪合万死。然 君臣之间。贵在无隐。既有所疑如是。若徒知隐讳。而不敢言。则何以明其情实。而有所解释乎。臣求得棨疏观之。似是只论 谥号叠用为可疑也。此不过泛论典礼耳。绝未见有讥贬之意也。至于再疏则实不为也。考日记可见矣。然则棨之不敢为讥贬。似可得而明之也。至于沈大孚之疏。臣亦恐其只论典礼耳。实无讥贬 先王之意
未及上进。伏见昨暮赵锡胤 批答之辞。乃伏审 圣心深怒棨等。蕴蓄已久。乃发于今日也。夫 圣意既以棨等为贬薄 先王。则其怒之也。乃怒所当怒也。于此益见 圣孝之至。窃不胜感激叹服之深也。而其言心中所蕴。罄尽如此。此诚所谓开心见诚。无所隐伏者。 君臣之间。相与罄尽如是。则岂复有疑间之存于其中哉。此尤帝王之盛节。尤不任叹服之至也。夫 殿下既罄尽如是。臣安敢不悉陈其心之所疑乎。 圣教谓棨再上疏章。初则辞意不至已甚。其再则敢举 庙号而斥言之。臣窃闻棨只为一疏。不为再疏。考之政院日记。亦然云。然则其再疏所言。必非棨所为也。臣窃恐 殿下于创巨之初。荒迷之际。见他人疏而认为棨疏也。臣敢疑 殿下荒迷之中有所不察。罪合万死。然 君臣之间。贵在无隐。既有所疑如是。若徒知隐讳。而不敢言。则何以明其情实。而有所解释乎。臣求得棨疏观之。似是只论 谥号叠用为可疑也。此不过泛论典礼耳。绝未见有讥贬之意也。至于再疏则实不为也。考日记可见矣。然则棨之不敢为讥贬。似可得而明之也。至于沈大孚之疏。臣亦恐其只论典礼耳。实无讥贬 先王之意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07H 页
 也。若棨与大孚相议为之。则臣决知其不然也。此两人素非相亲者。岂有素所不亲之人。相议以讥君父者乎。孔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夫诈与不信。人之甚可恶者也。其事近于诈与不信。则人之疑也固宜。然圣人戒之者。盖或有其事虽近于诈与不信。其情则实不诈而可信者。如此者。若逆亿而恶之。则岂不为害。故圣人惧此而戒之。圣人之言。岂非忠厚之至乎。孔子又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盖所恶者恶也。旧有恶者能改之。则为无恶矣。故许其今日之无恶。而不念旧日已改之恶也。圣人好恶之公。无所系滞如此。窃念 殿下罪棨等。岂有一毫私意哉。只为曾见其疏辞有不善。故痛疾矣。今知其疏不然。则诚宜洞然解释。无复系滞之私留于念虑之间。盖见可怒则怒。无可怒则待之无间。此正圣人廓然大公虚心待物之道也。如是则 圣心喜怒之正。群下谁不悦服而取则也哉。夫一民含冤而被罪。犹为王政之害。况侍从之臣。罪状未明。遽施投畀之典。其于用罚。岂不太过乎。此群情之所共闷郁者也。今悉知 圣意愤疾之所在。棨之情实。似有可以卞释者。故敢此冒渎。伏愿 圣明留神澄省焉。臣无任惶恐战慄
也。若棨与大孚相议为之。则臣决知其不然也。此两人素非相亲者。岂有素所不亲之人。相议以讥君父者乎。孔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夫诈与不信。人之甚可恶者也。其事近于诈与不信。则人之疑也固宜。然圣人戒之者。盖或有其事虽近于诈与不信。其情则实不诈而可信者。如此者。若逆亿而恶之。则岂不为害。故圣人惧此而戒之。圣人之言。岂非忠厚之至乎。孔子又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盖所恶者恶也。旧有恶者能改之。则为无恶矣。故许其今日之无恶。而不念旧日已改之恶也。圣人好恶之公。无所系滞如此。窃念 殿下罪棨等。岂有一毫私意哉。只为曾见其疏辞有不善。故痛疾矣。今知其疏不然。则诚宜洞然解释。无复系滞之私留于念虑之间。盖见可怒则怒。无可怒则待之无间。此正圣人廓然大公虚心待物之道也。如是则 圣心喜怒之正。群下谁不悦服而取则也哉。夫一民含冤而被罪。犹为王政之害。况侍从之臣。罪状未明。遽施投畀之典。其于用罚。岂不太过乎。此群情之所共闷郁者也。今悉知 圣意愤疾之所在。棨之情实。似有可以卞释者。故敢此冒渎。伏愿 圣明留神澄省焉。臣无任惶恐战慄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07L 页
 激切祈恳之至。
激切祈恳之至。进庸学困得疏
伏以臣愚陋朴拙。自少无他技能。惟幸知读四书。而窃究心焉。至粗有论说。虽不敢自是。乃是一生精力所在。不欲委弃。谨藏之箧笥。时时披阅。用以自喜。曾于春间。窃闻 殿下书筵进讲孟子。谨以所说论孟两书奉进。伏蒙 先王褒答。至于赐物以赏其微诚。至今思之。不胜悲感之至。顷者伏闻 筵席进讲中庸。即拟以所说庸学上献。而所有册乃是草本。涂改颇多。而稍精写者在乡。故迟延至此。今得改写。敢此上进。臣窃伏思论孟及庸学两篇。汉唐诸儒笺注纷然。论说愈多。而经义愈晦。至程朱子极力研索。直见本旨。备尽推说。以晓学者。而朱子著集注章句以传于世。则圣贤之旨。粲然明白。无复隐晦。如阴翳解散。大明中天也。夫先贤解释经义。如是其著明。后学惟当由是而求之。自可以见圣贤之旨也。臣之愚陋固滞。不安于泛读涉猎。必欲更求微意。沈潜不置。积以岁年。见旧说之外似更有多少微蕴。自皆呈露。恐其亡失。从而录之。臣之区区妄见。何敢自谓有得。然实竭其一生之力。窃恐或不无一得处也。今当 圣明
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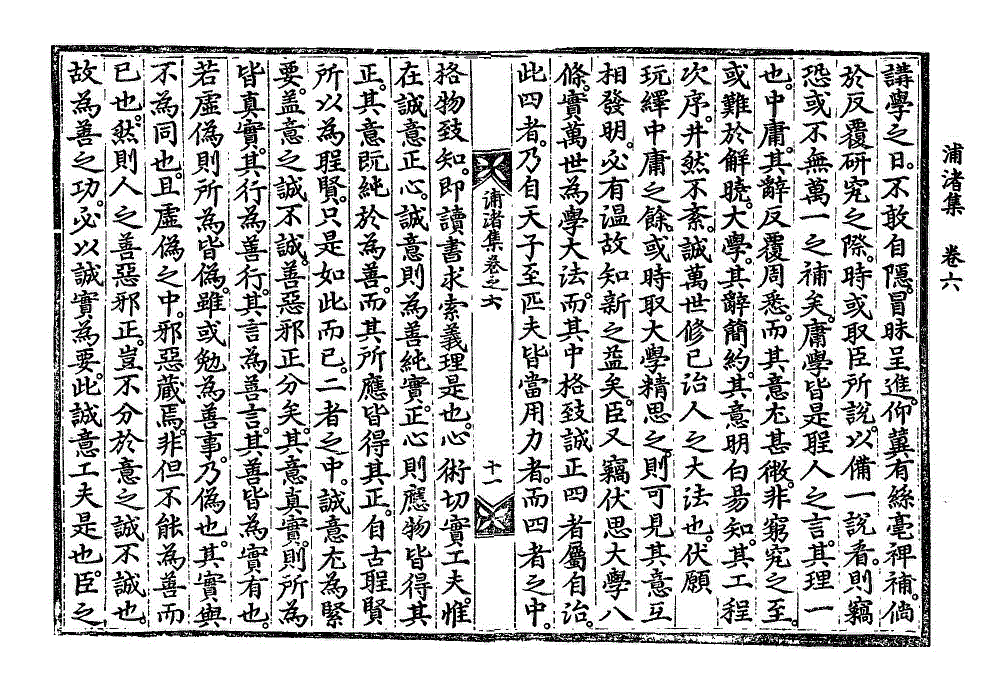 讲学之日。不敢自隐。冒昧呈进。仰冀有丝毫裨补。倘于反覆研究之际。时或取臣所说。以备一说看。则窃恐或不无万一之补矣。庸学皆是圣人之言。其理一也。中庸。其辞反覆周悉。而其意尤甚微。非穷究之至。或难于解晓。大学。其辞简约。其意明白易知。其工程次序。井然不紊。诚万世修己治人之大法也。伏愿 玩绎中庸之馀。或时取大学精思之。则可见其意互相发明。必有温故知新之益矣。臣又窃伏思大学八条。实万世为学大法。而其中格致诚正四者属自治。此四者。乃自天子至匹夫皆当用力者。而四者之中。格物致知。即读书求索义理是也。心术切实工夫。惟在诚意正心。诚意则为善纯实。正心则应物皆得其正。其意既纯于为善。而其所应皆得其正。自古圣贤所以为圣贤。只是如此而已。二者之中。诚意尤为紧要。盖意之诚不诚。善恶邪正分矣。其意真实。则所为皆真实。其行为善行。其言为善言。其善皆为实有也。若虚伪则所为皆伪。虽或勉为善事。乃伪也。其实与不为同也。且虚伪之中。邪恶藏焉。非但不能为善而已也。然则人之善恶邪正。岂不分于意之诚不诚也。故为善之功。必以诚实为要。此诚意工夫是也。臣之
讲学之日。不敢自隐。冒昧呈进。仰冀有丝毫裨补。倘于反覆研究之际。时或取臣所说。以备一说看。则窃恐或不无万一之补矣。庸学皆是圣人之言。其理一也。中庸。其辞反覆周悉。而其意尤甚微。非穷究之至。或难于解晓。大学。其辞简约。其意明白易知。其工程次序。井然不紊。诚万世修己治人之大法也。伏愿 玩绎中庸之馀。或时取大学精思之。则可见其意互相发明。必有温故知新之益矣。臣又窃伏思大学八条。实万世为学大法。而其中格致诚正四者属自治。此四者。乃自天子至匹夫皆当用力者。而四者之中。格物致知。即读书求索义理是也。心术切实工夫。惟在诚意正心。诚意则为善纯实。正心则应物皆得其正。其意既纯于为善。而其所应皆得其正。自古圣贤所以为圣贤。只是如此而已。二者之中。诚意尤为紧要。盖意之诚不诚。善恶邪正分矣。其意真实。则所为皆真实。其行为善行。其言为善言。其善皆为实有也。若虚伪则所为皆伪。虽或勉为善事。乃伪也。其实与不为同也。且虚伪之中。邪恶藏焉。非但不能为善而已也。然则人之善恶邪正。岂不分于意之诚不诚也。故为善之功。必以诚实为要。此诚意工夫是也。臣之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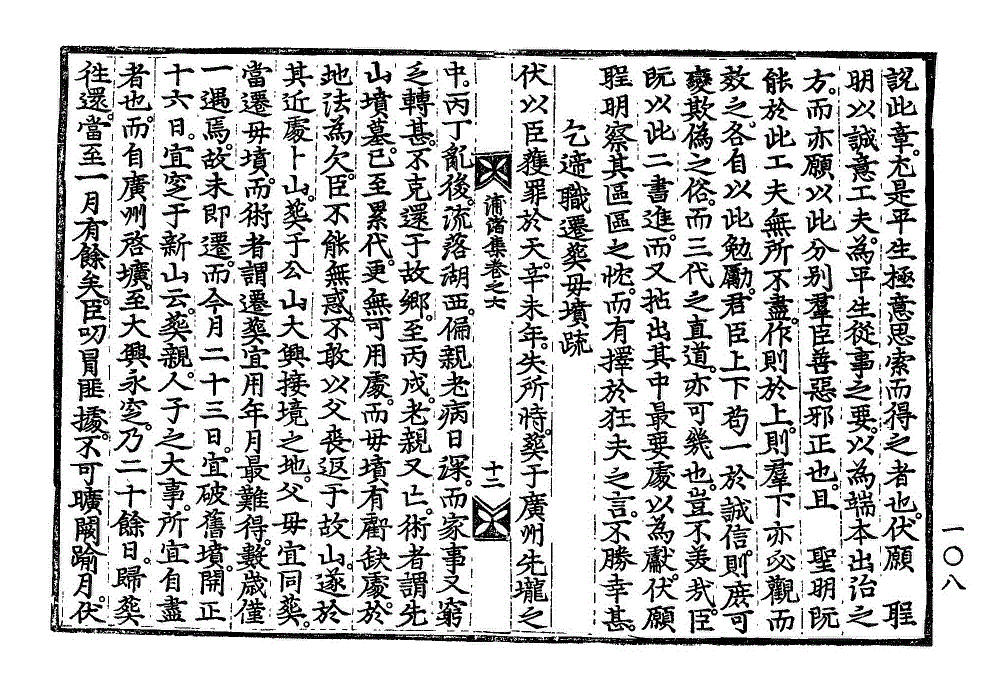 说此章。尤是平生极意思索而得之者也。伏愿 圣明以诚意工夫。为平生从事之要。以为端本出治之方。而亦愿以此分别群臣善恶邪正也。且 圣明既能于此工夫无所不尽。作则于上。则群下亦必观而效之。各自以此勉励。君臣上下苟一于诚信。则庶可变欺伪之俗。而三代之直道。亦可几也。岂不美哉。臣既以此二书进。而又拈出其中最要处以为献。伏愿圣明察其区区之忱。而有择于狂夫之言。不胜幸甚。
说此章。尤是平生极意思索而得之者也。伏愿 圣明以诚意工夫。为平生从事之要。以为端本出治之方。而亦愿以此分别群臣善恶邪正也。且 圣明既能于此工夫无所不尽。作则于上。则群下亦必观而效之。各自以此勉励。君臣上下苟一于诚信。则庶可变欺伪之俗。而三代之直道。亦可几也。岂不美哉。臣既以此二书进。而又拈出其中最要处以为献。伏愿圣明察其区区之忱。而有择于狂夫之言。不胜幸甚。乞递职迁葬母坟疏
伏以臣获罪于天。辛未年。失所恃。葬于广州先垄之中。丙丁乱后。流落湖西。偏亲老病日深。而家事又穷乏转甚。不克还于故乡。至丙戌。老亲又亡。术者谓先山坟墓。已至累代。更无可用处。而母坟有亏缺处。于地法为欠。臣不能无惑。不敢以父丧返于故山。遂于其近处卜山。葬于公山大兴接境之地。父母宜同葬。当迁母坟。而术者谓迁葬宜用年月最难得。数岁仅一遇焉。故未即迁。而今月二十三日。宜破旧坟。开正十六日。宜窆于新山云。葬亲。人子之大事。所宜自尽者也。而自广州启圹。至大兴永窆。乃二十馀日。归葬往还。当至一月有馀矣。臣叨冒匪据。不可旷阙踰月。伏
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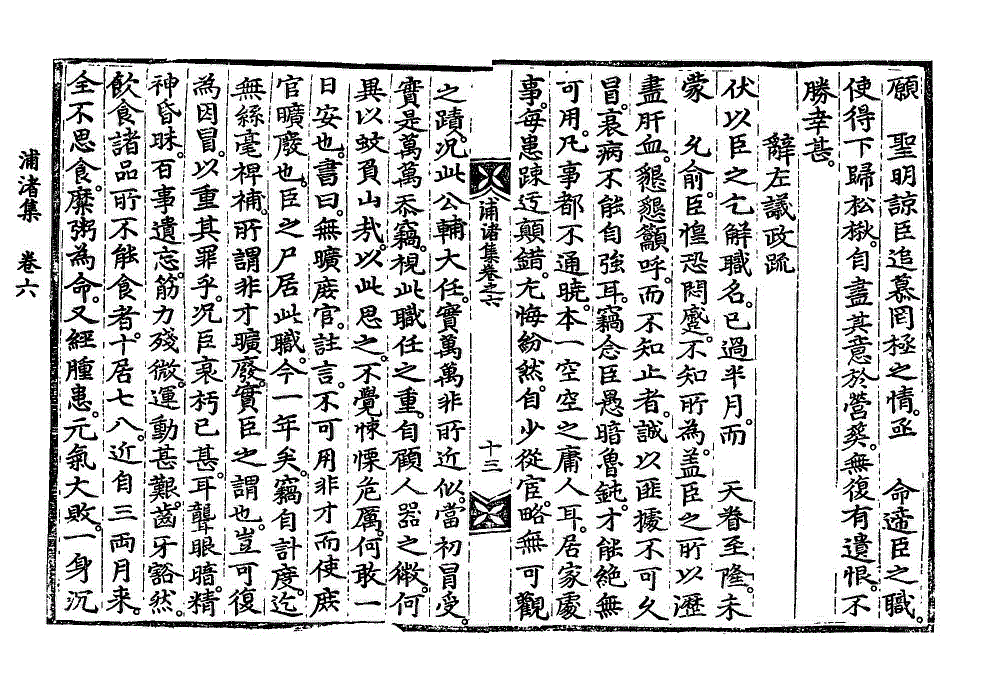 愿 圣明谅臣追慕罔极之情。亟 命递臣之职。使得下归松楸。自尽其意于营葬。无复有遗恨。不胜幸甚。
愿 圣明谅臣追慕罔极之情。亟 命递臣之职。使得下归松楸。自尽其意于营葬。无复有遗恨。不胜幸甚。辞左议政疏
伏以臣之乞解职名。已过半月。而 天眷至隆。未蒙 允俞。臣惶恐闷蹙。不知所为。盖臣之所以沥尽肝血。恳恳吁呼。而不知止者。诚以匪据不可久冒。衰病不能自强耳。窃念臣愚暗鲁钝。才能绝无可用。凡事都不通晓。本一空空之庸人耳。居家处事。每患疏迂颠错。尤悔纷然。自少从宦。略无可观之迹。况此公辅大任。实万万非所近似。当初冒受。实是万万忝窃。视此职任之重。自顾人器之微。何异以蚊负山哉。以此思之。不觉悚慄危厉。何敢一日安也。书曰。无旷庶官。注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旷废也。臣之尸居此职。今一年矣。窃自计度。迄无丝毫裨补。所谓非才旷废。实臣之谓也。岂可复为因冒。以重其罪乎。况臣衰朽已甚。耳聋眼暗。精神昏昧。百事遗忘。筋力残微。运动甚艰。齿牙豁然。饮食诸品所不能食者。十居七八。近自三两月来。全不思食。糜粥为命。又经肿患。元气大败。一身沈
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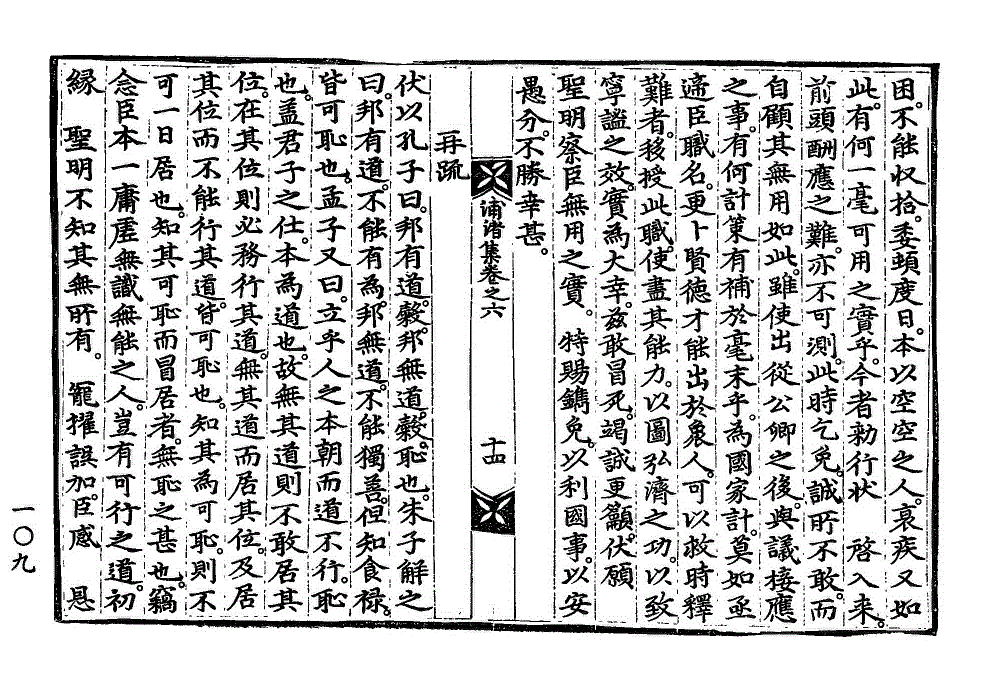 困。不能收拾。委顿度日。本以空空之人。衰疾又如此。有何一毫可用之实乎。今者敕行状 启入来。前头酬应之难。亦不可测。此时乞免。诚所不敢。而自顾其无用如此。虽使出从公卿之后。与议接应之事。有何计策有补于毫末乎。为国家计。莫如亟递臣职名。更卜贤德才能出于众人。可以救时释难者。移授此职。使尽其能力。以图弘济之功。以致宁谧之效。实为大幸。兹敢冒死。竭诚更吁。伏愿 圣明察臣无用之实。 特赐镌免。以利国事。以安愚分。不胜幸甚。
困。不能收拾。委顿度日。本以空空之人。衰疾又如此。有何一毫可用之实乎。今者敕行状 启入来。前头酬应之难。亦不可测。此时乞免。诚所不敢。而自顾其无用如此。虽使出从公卿之后。与议接应之事。有何计策有补于毫末乎。为国家计。莫如亟递臣职名。更卜贤德才能出于众人。可以救时释难者。移授此职。使尽其能力。以图弘济之功。以致宁谧之效。实为大幸。兹敢冒死。竭诚更吁。伏愿 圣明察臣无用之实。 特赐镌免。以利国事。以安愚分。不胜幸甚。辞左议政疏[再疏]
伏以孔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朱子解之曰。邦有道。不能有为。邦无道。不能独善。但知食禄。皆可耻也。孟子又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盖君子之仕。本为道也。故无其道则不敢居其位。在其位则必务行其道。无其道而居其位。及居其位而不能行其道。皆可耻也。知其为可耻。则不可一日居也。知其可耻而冒居者。无耻之甚也。窃念臣本一庸虚无识无能之人。岂有可行之道。初缘 圣明不知其无所有。 宠擢误加。臣感 恩
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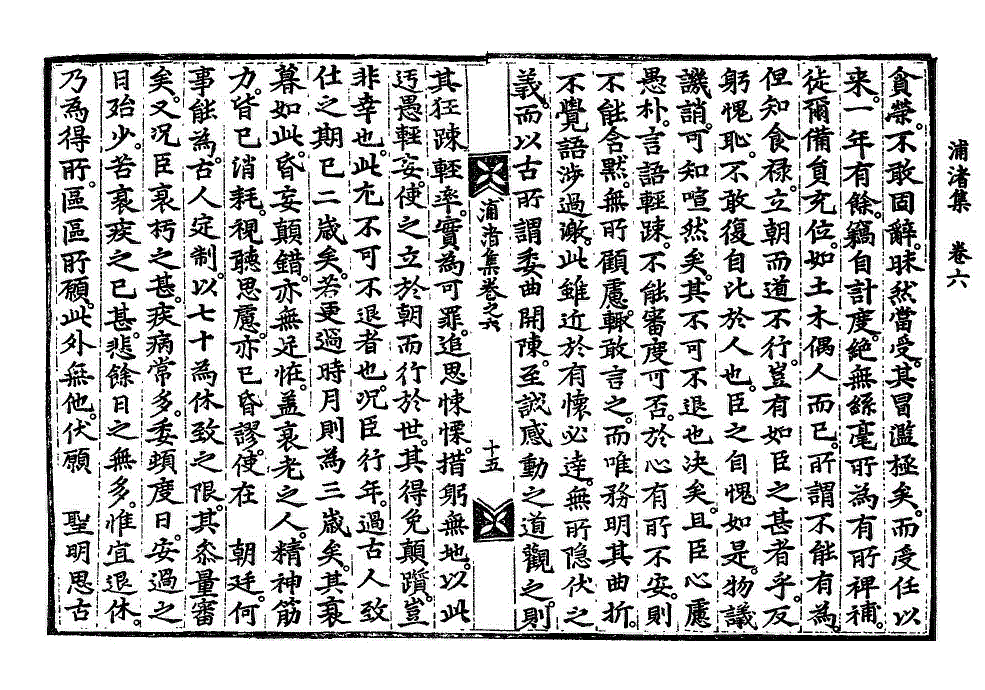 贪荣。不敢固辞。昧然当受。其冒滥极矣。而受任以来。一年有馀。窃自计度。绝无丝毫所为有所裨补。徒尔备员充位。如土木偶人而已。所谓不能有为。但知食禄。立朝而道不行。岂有如臣之甚者乎。反躬愧耻。不敢复自比于人也。臣之自愧如是。物议讥诮。可知喧然矣。其不可不退也决矣。且臣心虑愚朴。言语轻疏。不能审度可否。于心有所不安。则不能含默。无所顾虑。辄敢言之。而唯务明其曲折。不觉语涉过激。此虽近于有怀必达。无所隐伏之义。而以古所谓委曲开陈。至诚感动之道观之。则其狂疏轻率。实为可罪。追思悚慄。措躬无地。以此迂愚轻妄。使之立于朝而行于世。其得免颠踬。岂非幸也。此尤不可不退者也。况臣行年。过古人致仕之期已二岁矣。若更过时月则为三岁矣。其衰暮如此。昏妄颠错。亦无足怪。盖衰老之人。精神筋力。皆已消耗。视听思虑。亦已昏谬。使在 朝廷。何事能为。古人定制。以七十为休致之限。其参量审矣。又况臣衰朽之甚。疾病常多。委顿度日。安过之日殆少。苦衰疾之已甚。悲馀日之无多。惟宜退休。乃为得所。区区所愿。此外无他。伏愿 圣明思古
贪荣。不敢固辞。昧然当受。其冒滥极矣。而受任以来。一年有馀。窃自计度。绝无丝毫所为有所裨补。徒尔备员充位。如土木偶人而已。所谓不能有为。但知食禄。立朝而道不行。岂有如臣之甚者乎。反躬愧耻。不敢复自比于人也。臣之自愧如是。物议讥诮。可知喧然矣。其不可不退也决矣。且臣心虑愚朴。言语轻疏。不能审度可否。于心有所不安。则不能含默。无所顾虑。辄敢言之。而唯务明其曲折。不觉语涉过激。此虽近于有怀必达。无所隐伏之义。而以古所谓委曲开陈。至诚感动之道观之。则其狂疏轻率。实为可罪。追思悚慄。措躬无地。以此迂愚轻妄。使之立于朝而行于世。其得免颠踬。岂非幸也。此尤不可不退者也。况臣行年。过古人致仕之期已二岁矣。若更过时月则为三岁矣。其衰暮如此。昏妄颠错。亦无足怪。盖衰老之人。精神筋力。皆已消耗。视听思虑。亦已昏谬。使在 朝廷。何事能为。古人定制。以七十为休致之限。其参量审矣。又况臣衰朽之甚。疾病常多。委顿度日。安过之日殆少。苦衰疾之已甚。悲馀日之无多。惟宜退休。乃为得所。区区所愿。此外无他。伏愿 圣明思古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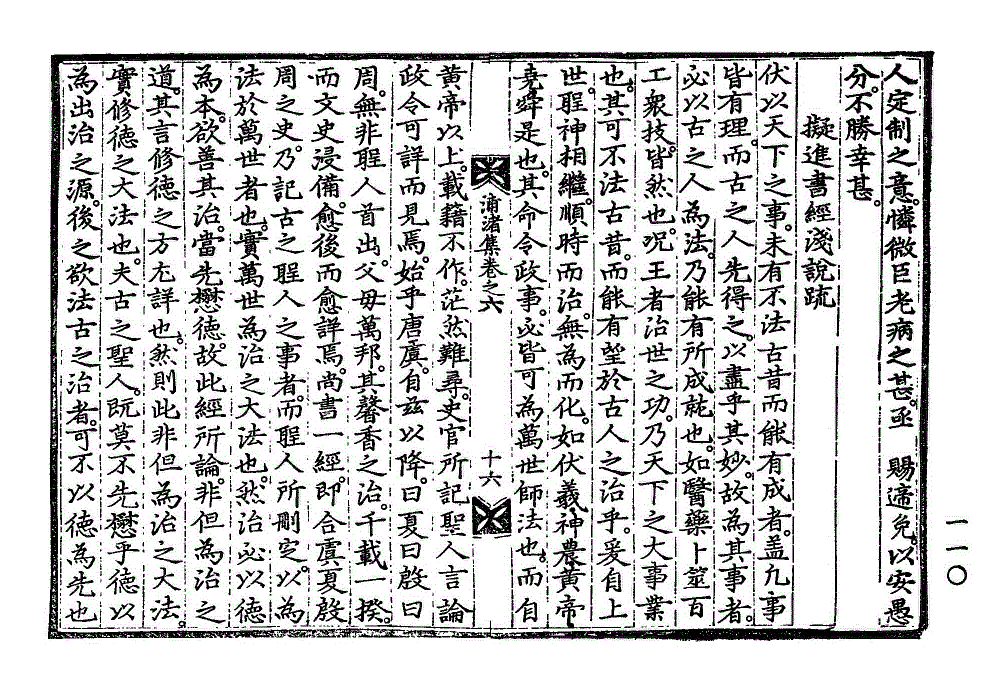 人定制之意。怜微臣老病之甚。亟 赐递免。以安愚分。不胜幸甚。
人定制之意。怜微臣老病之甚。亟 赐递免。以安愚分。不胜幸甚。拟进书经浅说疏
伏以天下之事。未有不法古昔而能有成者。盖凡事皆有理。而古之人先得之。以尽乎其妙。故为其事者。必以古之人为法。乃能有所成就也。如医药卜筮百工众技。皆然也。况王者治世之功。乃天下之大事业也。其可不法古昔。而能有望于古人之治乎。爰自上世。圣神相继。顺时而治。无为而化。如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是也。其命令政事。必皆可为万世师法也。而自黄帝以上。载籍不作。茫然难寻。史官所记圣人言论政令可详而见焉。始乎唐虞。自兹以降。曰夏曰殷曰周。无非圣人首出。父母万邦。其馨香之治。千载一揆。而文史浸备。愈后而愈详焉。尚书一经。即合虞夏殷周之史。乃记古之圣人之事者。而圣人所删定。以为法于万世者也。实万世为治之大法也。然治必以德为本。欲善其治。当先懋德。故此经所论。非但为治之道。其言修德之方尤详也。然则此非但为治之大法。实修德之大法也。夫古之圣人。既莫不先懋乎德以为出治之源。后之欲法古之治者。可不以德为先也
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11H 页
 哉。臣向在畎亩。读是经。见其于传注之外尚有馀意未发者。敢录之为说也。盖其事为诰命。未见有馀意处。不敢强说。而惟其君臣之间相与论德论治之语。似多有微意蕴蓄者。区区所说。只在此等处耳。夫千载上圣人微蕴。岂如臣末学固陋所能窥闯。第以积年辛勤探索而得之。窃恐其或未必不为千虑之一得也。敢书而藏之。今遭逢 圣明。叨冒至此。尧舜吾君。乃其责也。而目今 筵席。以此经进讲。法古为治。此正其机也。区区所望于 圣明。岂在三代下哉。因窃伏思前日所说。虽不足观。亦恐或不无万一裨补也。虽其仰尘 天听。难逃僭越之罪。若终闭匿不进。亦区区微诚所不敢安。兹敢冒昧上进。倘于 乙夜之间寻绎之际。或 赐省览。则亦或可以备好察迩言之一也。
哉。臣向在畎亩。读是经。见其于传注之外尚有馀意未发者。敢录之为说也。盖其事为诰命。未见有馀意处。不敢强说。而惟其君臣之间相与论德论治之语。似多有微意蕴蓄者。区区所说。只在此等处耳。夫千载上圣人微蕴。岂如臣末学固陋所能窥闯。第以积年辛勤探索而得之。窃恐其或未必不为千虑之一得也。敢书而藏之。今遭逢 圣明。叨冒至此。尧舜吾君。乃其责也。而目今 筵席。以此经进讲。法古为治。此正其机也。区区所望于 圣明。岂在三代下哉。因窃伏思前日所说。虽不足观。亦恐或不无万一裨补也。虽其仰尘 天听。难逃僭越之罪。若终闭匿不进。亦区区微诚所不敢安。兹敢冒昧上进。倘于 乙夜之间寻绎之际。或 赐省览。则亦或可以备好察迩言之一也。请李,成两贤臣文庙从祀疏。
伏以臣伏见馆学儒生以先正臣李珥,成浑从祀 文庙事。伏 阙陈疏今已累日。而未蒙 允俞。臣等窃念此乃斯文重事。岂独儒生之责任。当自 朝廷议定。臣等不敢默默。仰陈所怀。盖人之善。有大小高下。故孟子有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
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11L 页
 之说。其善高于一州一道而已者。何可祀于 文庙乎。不合祀于 文庙而祀焉。其为僭孰甚焉。使死者有知。其神岂能安于幽冥之中乎。是其祀之者非所以尊之。而亦且得罪于 文庙矣。若其善高于一世。可以为百代师表。则其宜祀于 文庙也必矣。如是而不得祀焉。则其为斯文之欠阙实大。而为群士之恨宜矣。臣等虽不及亲炙于二贤。然其学问行义之实。则闻之熟矣。李珥天禀之高。所学之正。识见之超诣。德行之纯备。实可谓三代人物。而可以为百代之师表矣。臣等非平生诚服之至。何敢阿所好。而为欺罔乎。成浑其高明透彻。虽若不及于李珥。而端庄严重则李珥常自谓不及。一生读圣贤书。凡居家践履。出处行事。一以圣贤为法。诚所谓儒者之高蹈也。此二臣之德。其宜祀于 文庙者。实百世不可易之论也。多士之请。出于秉彝好德之情。可见今之士子趋向之得其正也。深为可嘉也。 殿下不即允从者。必以从祀事体至重。不可以儒生之论轻易许之也。乃慎重之意也。然亦窃恐 殿下于二臣之德。知之未深也。今此儒生之论。一时不谋而同者。如是其众。至于外方。闻风而来者。日益多。亦可见人心之所同也。
之说。其善高于一州一道而已者。何可祀于 文庙乎。不合祀于 文庙而祀焉。其为僭孰甚焉。使死者有知。其神岂能安于幽冥之中乎。是其祀之者非所以尊之。而亦且得罪于 文庙矣。若其善高于一世。可以为百代师表。则其宜祀于 文庙也必矣。如是而不得祀焉。则其为斯文之欠阙实大。而为群士之恨宜矣。臣等虽不及亲炙于二贤。然其学问行义之实。则闻之熟矣。李珥天禀之高。所学之正。识见之超诣。德行之纯备。实可谓三代人物。而可以为百代之师表矣。臣等非平生诚服之至。何敢阿所好。而为欺罔乎。成浑其高明透彻。虽若不及于李珥。而端庄严重则李珥常自谓不及。一生读圣贤书。凡居家践履。出处行事。一以圣贤为法。诚所谓儒者之高蹈也。此二臣之德。其宜祀于 文庙者。实百世不可易之论也。多士之请。出于秉彝好德之情。可见今之士子趋向之得其正也。深为可嘉也。 殿下不即允从者。必以从祀事体至重。不可以儒生之论轻易许之也。乃慎重之意也。然亦窃恐 殿下于二臣之德。知之未深也。今此儒生之论。一时不谋而同者。如是其众。至于外方。闻风而来者。日益多。亦可见人心之所同也。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12H 页
 且此非但儒生之论也。实举世之论也。 殿下若以臣等之言为不足信。则请问于凡诸臣 殿下所信者。则必皆以臣等之言为是也。不幸士论携贰。固曾有诋毁二臣者矣。然程朱之时。亦有疾害之者。此岂害于举世之尊之也。今当 圣明崇儒重道之日。二臣从祀之请。不得蒙 允许。则岂不为圣代之欠事也。伏愿 圣明深察二臣之德实可为百世之师表。而举世同然之情。不可强拂也。霈然许其所请。不胜幸甚。
且此非但儒生之论也。实举世之论也。 殿下若以臣等之言为不足信。则请问于凡诸臣 殿下所信者。则必皆以臣等之言为是也。不幸士论携贰。固曾有诋毁二臣者矣。然程朱之时。亦有疾害之者。此岂害于举世之尊之也。今当 圣明崇儒重道之日。二臣从祀之请。不得蒙 允许。则岂不为圣代之欠事也。伏愿 圣明深察二臣之德实可为百世之师表。而举世同然之情。不可强拂也。霈然许其所请。不胜幸甚。卞柳㮨欺罔疏
伏以臣闻。古人云。圣人不世出。贤人不时出。盖圣贤之生。必得天地纯粹之气而生。天地之气纯粹者至少。驳杂者至多。故圣贤之生。不能每世每时而出。间数百载乃出。孔孟之后历千数百年。而得程朱子焉。夫程朱子所以能得孔孟之学。只是得之于遗经也。所谓遗经者。五经语孟是也。是书也世所多有。人皆见之。然由是书而能得圣人之学。历千数百年而始有焉。岂非禀纯粹之气者世所极罕也。东方自丽朝。文学大盛。惟圣贤义理之学则未闻也。至 本朝。赵光祖,李滉始以圣贤为学。或进而有为于朝。或退而
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12L 页
 自修于家。其学问道德。皆可为百世师表。其后又有李珥成浑。其强学力行。修诸身而行之家。至于立朝进退事 君及民之道。一以圣贤为法。夫圣贤学问。世所极罕。况我海外陋邦。能为古人之学者。尤所绝少。举世所不为之事。谁劝谁教。而此数人能慨然有慕于古。独就遗经中寻究而得之。能自树立。以古人自处。实所谓豪杰之士也。非禀天地间世之气者。能然乎。不幸朝论携贰。其悦服尊慕者固多。而疾之者亦多。自古贤人君子之生于世也。必有以同德而为邻者矣。亦必有媢疾之人与之为冰炭也。孔子以乡人皆好皆恶为未可。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为可。然则无好无恶。皆非君子也。必有好之者。又有恶之者。乃君子也。非但两臣同时有恶之者。死后数十年。而其恶之者之党类子孙又绍述之。疾之愈甚。邪正相仇。其亦甚矣乎。两臣从祀之请。前后儒生。几至举国同然。湖南濒海之人。关西义州之人亦来去。京各千有馀里。其不谋而同如此。夫两臣皆是一孤踪寒儒。其生前死后。被人陷害极矣。有何一毫势力。而国中向慕。愈久愈深。可见两臣之贤。深为人所悦服。而秉彝好德出于天性者。人所同然也。独有疾之者之
自修于家。其学问道德。皆可为百世师表。其后又有李珥成浑。其强学力行。修诸身而行之家。至于立朝进退事 君及民之道。一以圣贤为法。夫圣贤学问。世所极罕。况我海外陋邦。能为古人之学者。尤所绝少。举世所不为之事。谁劝谁教。而此数人能慨然有慕于古。独就遗经中寻究而得之。能自树立。以古人自处。实所谓豪杰之士也。非禀天地间世之气者。能然乎。不幸朝论携贰。其悦服尊慕者固多。而疾之者亦多。自古贤人君子之生于世也。必有以同德而为邻者矣。亦必有媢疾之人与之为冰炭也。孔子以乡人皆好皆恶为未可。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为可。然则无好无恶。皆非君子也。必有好之者。又有恶之者。乃君子也。非但两臣同时有恶之者。死后数十年。而其恶之者之党类子孙又绍述之。疾之愈甚。邪正相仇。其亦甚矣乎。两臣从祀之请。前后儒生。几至举国同然。湖南濒海之人。关西义州之人亦来去。京各千有馀里。其不谋而同如此。夫两臣皆是一孤踪寒儒。其生前死后。被人陷害极矣。有何一毫势力。而国中向慕。愈久愈深。可见两臣之贤。深为人所悦服。而秉彝好德出于天性者。人所同然也。独有疾之者之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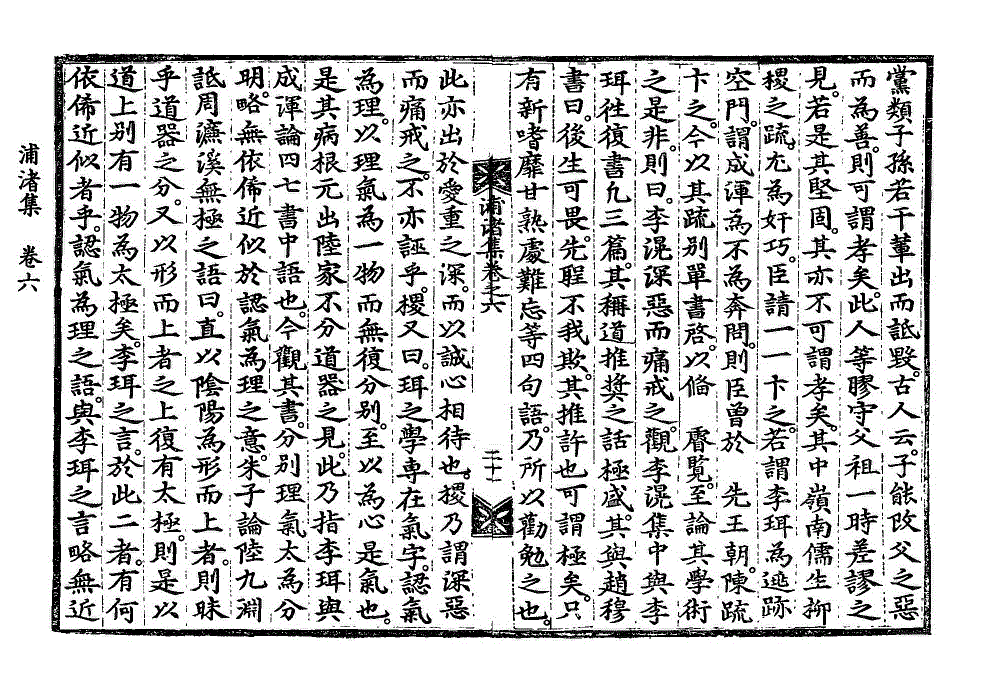 党类子孙若干辈出而诋毁。古人云。子能改父之恶而为善。则可谓孝矣。此人等胶守父祖一时差谬之见。若是其坚固。其亦不可谓孝矣。其中岭南儒生柳㮨之疏。尤为奸巧。臣请一一卞之。若谓李珥为逃迹空门。谓成浑为不为奔问。则臣曾于 先王朝。陈疏卞之。今以其疏别单书启。以备 睿览。至论其学术之是非。则曰。李滉深恶而痛戒之。观李滉集中与李珥往复书凡三篇。其称道推奖之话极盛。其与赵穆书曰。后生可畏。先圣不我欺。其推许也可谓极矣。只有新嗜靡甘熟处难忘等四句语。乃所以劝勉之也。此亦出于爱重之深。而以诚心相待也。㮨乃谓深恶而痛戒之。不亦诬乎。㮨又曰。珥之学专在气字。认气为理。以理气为一物而无复分别。至以为心是气也。是其病根元出陆家不分道器之见。此乃指李珥与成浑论四七书中语也。今观其书。分别理气太为分明。略无依俙近似于认气为理之意。朱子论陆九渊诋周濂溪无极之语曰。直以阴阳为形而上者。则昧乎道器之分。又以形而上者之上复有太极。则是以道上别有一物为太极矣。李珥之言。于此二者。有何依俙近似者乎。认气为理之语。与李珥之言略无近
党类子孙若干辈出而诋毁。古人云。子能改父之恶而为善。则可谓孝矣。此人等胶守父祖一时差谬之见。若是其坚固。其亦不可谓孝矣。其中岭南儒生柳㮨之疏。尤为奸巧。臣请一一卞之。若谓李珥为逃迹空门。谓成浑为不为奔问。则臣曾于 先王朝。陈疏卞之。今以其疏别单书启。以备 睿览。至论其学术之是非。则曰。李滉深恶而痛戒之。观李滉集中与李珥往复书凡三篇。其称道推奖之话极盛。其与赵穆书曰。后生可畏。先圣不我欺。其推许也可谓极矣。只有新嗜靡甘熟处难忘等四句语。乃所以劝勉之也。此亦出于爱重之深。而以诚心相待也。㮨乃谓深恶而痛戒之。不亦诬乎。㮨又曰。珥之学专在气字。认气为理。以理气为一物而无复分别。至以为心是气也。是其病根元出陆家不分道器之见。此乃指李珥与成浑论四七书中语也。今观其书。分别理气太为分明。略无依俙近似于认气为理之意。朱子论陆九渊诋周濂溪无极之语曰。直以阴阳为形而上者。则昧乎道器之分。又以形而上者之上复有太极。则是以道上别有一物为太极矣。李珥之言。于此二者。有何依俙近似者乎。认气为理之语。与李珥之言略无近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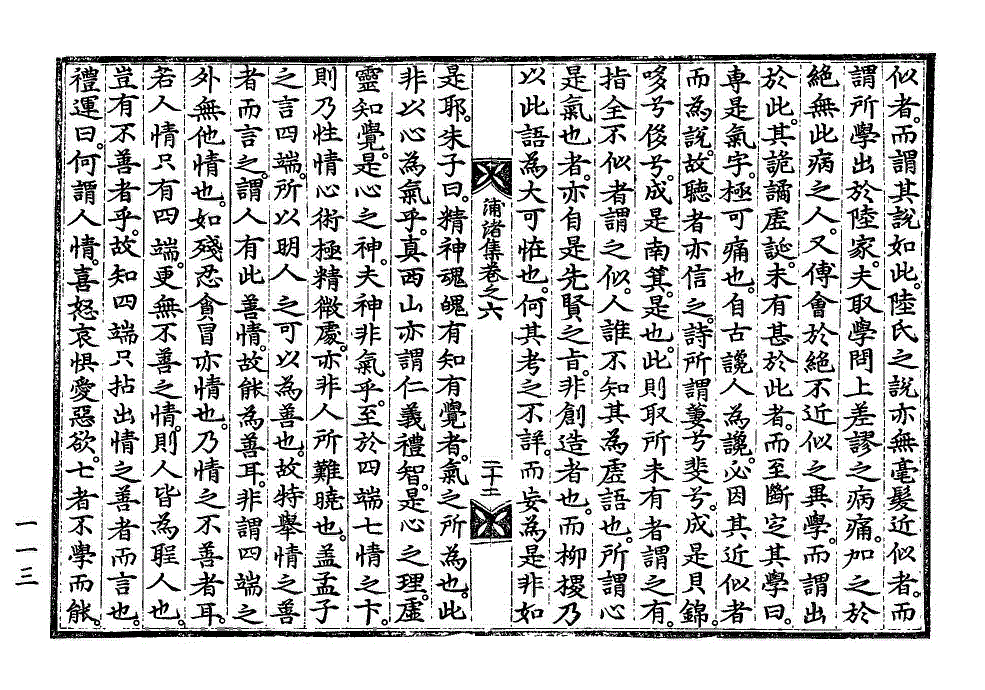 似者。而谓其说如此。陆氏之说亦无毫发近似者。而谓所学出于陆家。夫取学问上差谬之病痛。加之于绝无此病之人。又傅会于绝不近似之异学。而谓出于此。其诡谲虚诞。未有甚于此者。而至断定其学曰。专是气字。极可痛也。自古谗人为谗。必因其近似者而为说。故听者亦信之。诗所谓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是也。此则取所未有者谓之有。指全不似者谓之似。人谁不知其为虚语也。所谓心是气也者。亦自是先贤之旨。非创造者也。而柳㮨乃以此语为大可怪也。何其考之不详。而妄为是非如是耶。朱子曰。精神魂魄有知有觉者。气之所为也。此非以心为气乎。真西山亦谓仁义礼智。是心之理。虚灵知觉。是心之神。夫神非气乎。至于四端七情之卞。则乃性情心术极精微处。亦非人所难晓也。盖孟子之言四端。所以明人之可以为善也。故特举情之善者而言之。谓人有此善情。故能为善耳。非谓四端之外无他情也。如残忍贪冒亦情也。乃情之不善者耳。若人情只有四端。更无不善之情。则人皆为圣人也。岂有不善者乎。故知四端只拈出情之善者而言也。礼运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不学而能。
似者。而谓其说如此。陆氏之说亦无毫发近似者。而谓所学出于陆家。夫取学问上差谬之病痛。加之于绝无此病之人。又傅会于绝不近似之异学。而谓出于此。其诡谲虚诞。未有甚于此者。而至断定其学曰。专是气字。极可痛也。自古谗人为谗。必因其近似者而为说。故听者亦信之。诗所谓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是也。此则取所未有者谓之有。指全不似者谓之似。人谁不知其为虚语也。所谓心是气也者。亦自是先贤之旨。非创造者也。而柳㮨乃以此语为大可怪也。何其考之不详。而妄为是非如是耶。朱子曰。精神魂魄有知有觉者。气之所为也。此非以心为气乎。真西山亦谓仁义礼智。是心之理。虚灵知觉。是心之神。夫神非气乎。至于四端七情之卞。则乃性情心术极精微处。亦非人所难晓也。盖孟子之言四端。所以明人之可以为善也。故特举情之善者而言之。谓人有此善情。故能为善耳。非谓四端之外无他情也。如残忍贪冒亦情也。乃情之不善者耳。若人情只有四端。更无不善之情。则人皆为圣人也。岂有不善者乎。故知四端只拈出情之善者而言也。礼运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不学而能。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14H 页
 中庸曰。善怒哀乐。程子曰。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既谓人情有七。则此总人情而言也。此外更无他情也。圣人之情。有此七者而已。恶人之情。亦有此七者而已。惟七情中有善者。有恶者。圣人。有其善而无其恶。恶人。有其恶而失其善耳。七情之善者非四端乎。故四端。拈情之善者而言也。七情。总言人情也。善者恶者皆在其中也。若举七情之恶者。与四端为对则可。如以残忍对恻隐。以贪冒对羞恶。盖怒恶之不正者为残忍。爱欲之不正者为贪冒也。若以四端与七情为对则不可。七情之善者是四端也。七情中自有四端。何可谓之相对。此理虽若甚微。亦似分明。人苟不主先入。虚心思之则可皆知之也。李滉四七相对之论。苟精思之。则亦窃恐其未免为少差也。夫义理。天下之公也。学者穷理之功。所以沈潜研索。只是求义理之实。若于义理心有所疑。而恐违先贤。不为卞析。则此理终晦而不明。穷理之功。岂当如是乎。故虽先贤之言。苟于理有差。则惟当明其理而已。不可以违于先贤而不敢言也。昔程子作易传。乃竭其一生之精力也。而朱子指其差误处甚多。如观卦盥而不荐。伊川以为灌鬯之初。诚意犹存。朱子谓盥只
中庸曰。善怒哀乐。程子曰。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既谓人情有七。则此总人情而言也。此外更无他情也。圣人之情。有此七者而已。恶人之情。亦有此七者而已。惟七情中有善者。有恶者。圣人。有其善而无其恶。恶人。有其恶而失其善耳。七情之善者非四端乎。故四端。拈情之善者而言也。七情。总言人情也。善者恶者皆在其中也。若举七情之恶者。与四端为对则可。如以残忍对恻隐。以贪冒对羞恶。盖怒恶之不正者为残忍。爱欲之不正者为贪冒也。若以四端与七情为对则不可。七情之善者是四端也。七情中自有四端。何可谓之相对。此理虽若甚微。亦似分明。人苟不主先入。虚心思之则可皆知之也。李滉四七相对之论。苟精思之。则亦窃恐其未免为少差也。夫义理。天下之公也。学者穷理之功。所以沈潜研索。只是求义理之实。若于义理心有所疑。而恐违先贤。不为卞析。则此理终晦而不明。穷理之功。岂当如是乎。故虽先贤之言。苟于理有差。则惟当明其理而已。不可以违于先贤而不敢言也。昔程子作易传。乃竭其一生之精力也。而朱子指其差误处甚多。如观卦盥而不荐。伊川以为灌鬯之初。诚意犹存。朱子谓盥只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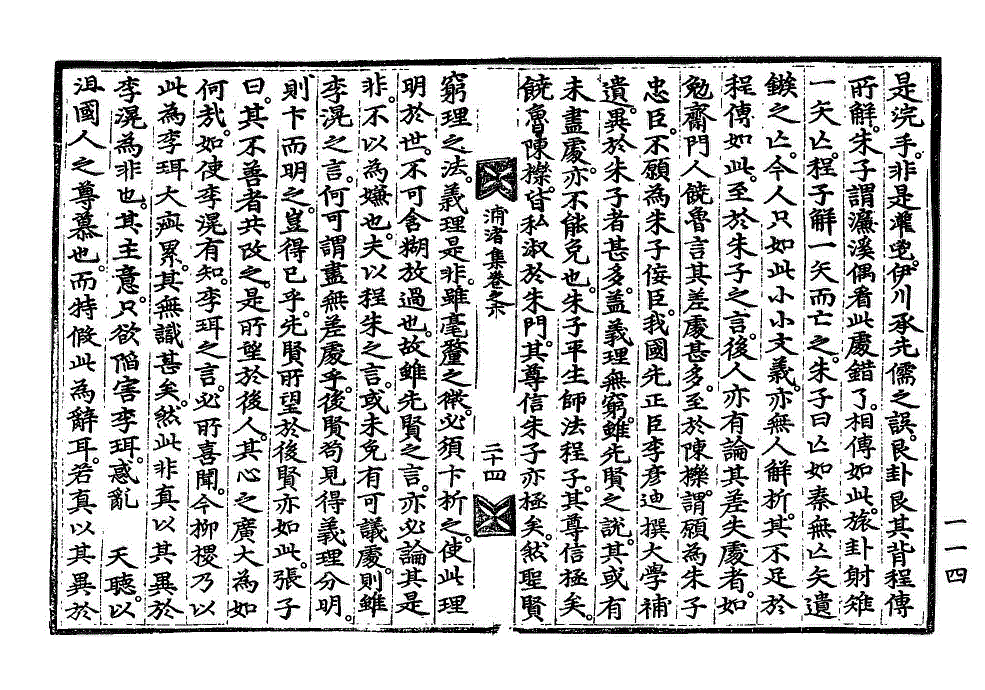 是浣手。非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误。艮卦艮其背程传所解。朱子谓濂溪偶看此处错了。相传如此。旅卦射雉一矢亡。程子解一矢而亡之。朱子曰亡如秦无亡矢遗镞之亡。今人只如此小小文义。亦无人解析。其不足于程传如此。至于朱子之言。后人亦有论其差失处者。如勉斋门人饶鲁言其差处甚多。至于陈栎。谓愿为朱子忠臣。不愿为朱子佞臣。我国先正臣李彦迪撰大学补遗。异于朱子者甚多。盖义理无穷。虽先贤之说。其或有未尽处。亦不能免也。朱子平生师法程子。其尊信极矣。饶鲁,陈栎。皆私淑于朱门。其尊信朱子亦极矣。然圣贤穷理之法。义理是非。虽毫釐之微。必须卞析之。使此理明于世。不可含糊放过也。故虽先贤之言。亦必论其是非。不以为嫌也。夫以程朱之言。或未免有可议处。则虽李滉之言。何可谓尽无差处乎。后贤苟见得义理分明。则卞而明之。岂得已乎。先贤所望于后贤亦如此。张子曰。其不善者共改之。是所望于后人。其心之广大为如何哉。如使李滉有知。李珥之言。必所喜闻。今柳㮨乃以此为李珥大疵累。其无识甚矣。然此非真以其异于李滉为非也。其主意。只欲陷害李珥。惑乱 天听。以沮国人之尊慕也。而特假此为辞耳。若真以其异于
是浣手。非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误。艮卦艮其背程传所解。朱子谓濂溪偶看此处错了。相传如此。旅卦射雉一矢亡。程子解一矢而亡之。朱子曰亡如秦无亡矢遗镞之亡。今人只如此小小文义。亦无人解析。其不足于程传如此。至于朱子之言。后人亦有论其差失处者。如勉斋门人饶鲁言其差处甚多。至于陈栎。谓愿为朱子忠臣。不愿为朱子佞臣。我国先正臣李彦迪撰大学补遗。异于朱子者甚多。盖义理无穷。虽先贤之说。其或有未尽处。亦不能免也。朱子平生师法程子。其尊信极矣。饶鲁,陈栎。皆私淑于朱门。其尊信朱子亦极矣。然圣贤穷理之法。义理是非。虽毫釐之微。必须卞析之。使此理明于世。不可含糊放过也。故虽先贤之言。亦必论其是非。不以为嫌也。夫以程朱之言。或未免有可议处。则虽李滉之言。何可谓尽无差处乎。后贤苟见得义理分明。则卞而明之。岂得已乎。先贤所望于后贤亦如此。张子曰。其不善者共改之。是所望于后人。其心之广大为如何哉。如使李滉有知。李珥之言。必所喜闻。今柳㮨乃以此为李珥大疵累。其无识甚矣。然此非真以其异于李滉为非也。其主意。只欲陷害李珥。惑乱 天听。以沮国人之尊慕也。而特假此为辞耳。若真以其异于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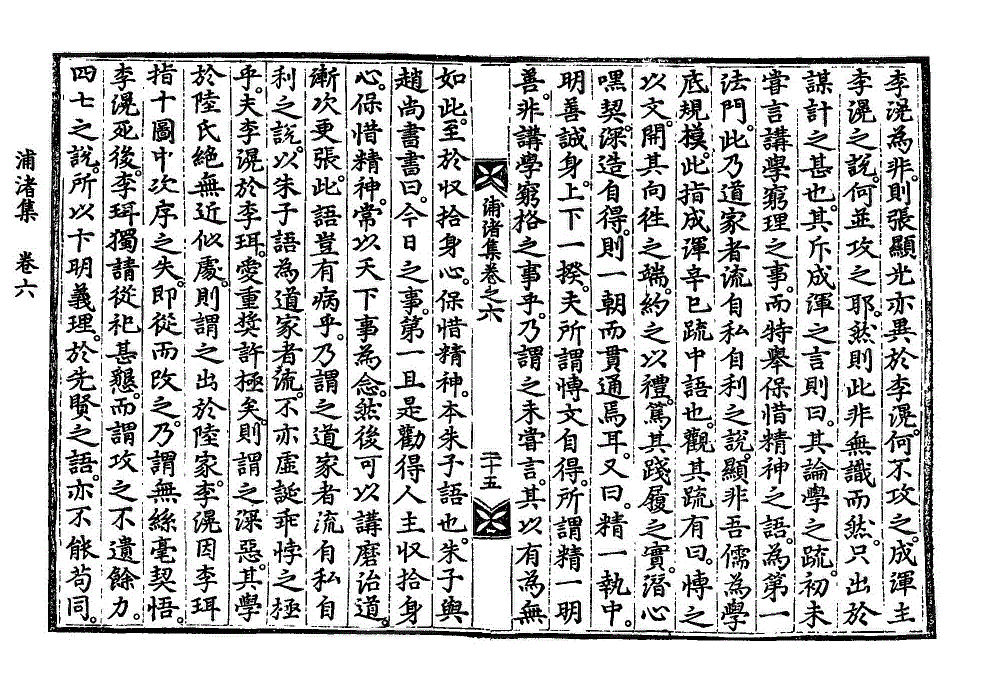 李滉为非。则张显光亦异于李滉。何不攻之。成浑主李滉之说。何并攻之耶。然则此非无识而然。只出于谋计之甚也。其斥成浑之言则曰。其论学之疏。初未尝言讲学穷理之事。而特举保惜精神之语。为第一法门。此乃道家者流自私自利之说。显非吾儒为学底规模。此指成浑辛巳疏中语也。观其疏有曰。博之以文。开其向往之端。约之以礼。笃其践履之实。潜心默契。深造自得。则一朝而贯通焉耳。又曰。精一执中。明善诚身。上下一揆。夫所谓博文自得。所谓精一明善。非讲学穷格之事乎。乃谓之未尝言。其以有为无如此。至于收拾身心。保惜精神。本朱子语也。朱子与赵尚书书曰。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劝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为念。然后可以讲磨治道。渐次更张。此语岂有病乎。乃谓之道家者流自私自利之说。以朱子语为道家者流。不亦虚诞乖悖之极乎。夫李滉于李珥。爱重奖许极矣。则谓之深恶。其学于陆氏绝无近似处。则谓之出于陆家。李滉因李珥指十图中次序之失。即从而改之。乃谓无丝毫契悟。李滉死后。李珥独请从祀甚恳。而谓攻之不遗馀力。四七之说。所以卞明义理。于先贤之语。亦不能苟同。
李滉为非。则张显光亦异于李滉。何不攻之。成浑主李滉之说。何并攻之耶。然则此非无识而然。只出于谋计之甚也。其斥成浑之言则曰。其论学之疏。初未尝言讲学穷理之事。而特举保惜精神之语。为第一法门。此乃道家者流自私自利之说。显非吾儒为学底规模。此指成浑辛巳疏中语也。观其疏有曰。博之以文。开其向往之端。约之以礼。笃其践履之实。潜心默契。深造自得。则一朝而贯通焉耳。又曰。精一执中。明善诚身。上下一揆。夫所谓博文自得。所谓精一明善。非讲学穷格之事乎。乃谓之未尝言。其以有为无如此。至于收拾身心。保惜精神。本朱子语也。朱子与赵尚书书曰。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劝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为念。然后可以讲磨治道。渐次更张。此语岂有病乎。乃谓之道家者流自私自利之说。以朱子语为道家者流。不亦虚诞乖悖之极乎。夫李滉于李珥。爱重奖许极矣。则谓之深恶。其学于陆氏绝无近似处。则谓之出于陆家。李滉因李珥指十图中次序之失。即从而改之。乃谓无丝毫契悟。李滉死后。李珥独请从祀甚恳。而谓攻之不遗馀力。四七之说。所以卞明义理。于先贤之语。亦不能苟同。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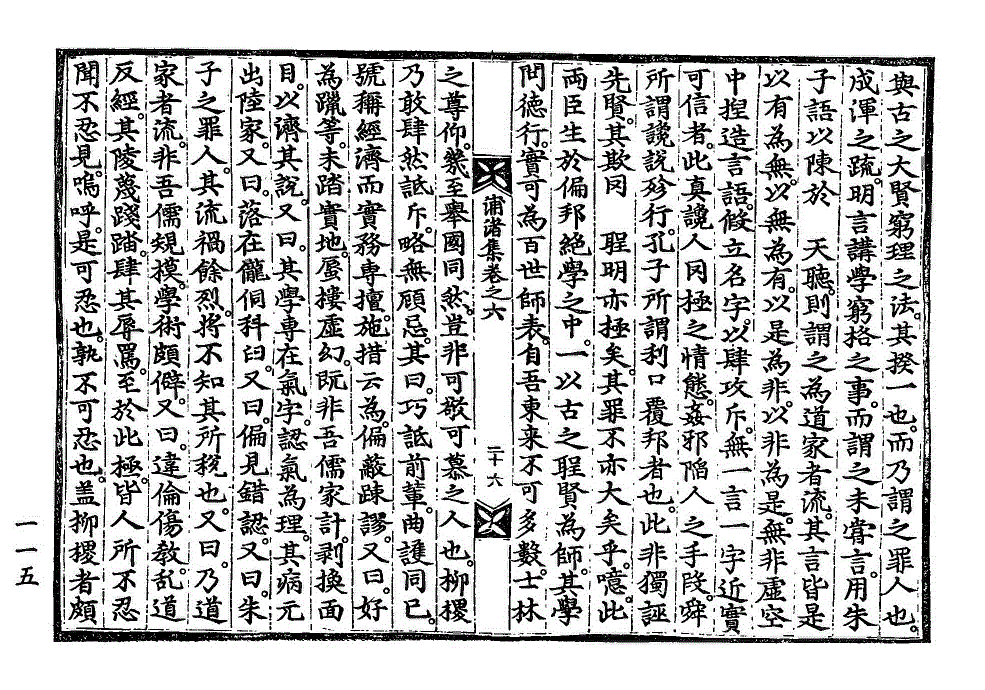 与古之大贤穷理之法。其揆一也。而乃谓之罪人也。成浑之疏。明言讲学穷格之事。而谓之未尝言。用朱子语以陈于 天听。则谓之为道家者流。其言皆是以有为无。以无为有。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无非虚空中捏造言语。假立名字。以肆攻斥。无一言一字近实可信者。此真谗人罔极之情态。奸邪陷人之手段。舜所谓谗说殄行。孔子所谓利口覆邦者也。此非独诬先贤。其欺罔 圣明亦极矣。其罪不亦大矣乎。噫。此两臣生于偏邦绝学之中。一以古之圣贤为师。其学问德行。实可为百世师表。自吾东来不可多数。士林之尊仰。几至举国同然。岂非可敬可慕之人也。柳㮨乃敢肆然诋斥。略无顾忌。其曰。巧诋前辈。曲謢同己。号称经济而实务专擅。施措云为。偏蔽疏谬。又曰。好为躐等。未踏实地。蜃楼虚幻。既非吾儒家计。剥换面目。以济其说。又曰。其学专在气字。认气为理。其病元出陆家。又曰。落在儱侗科臼。又曰。偏见错认。又曰。朱子之罪人。其流祸馀烈。将不知其所税也。又曰。乃道家者流。非吾儒规模。学术颇僻。又曰。违伦伤教。乱道反经。其陵蔑践踏。肆其辱骂。至于此极。皆人所不忍闻不忍见。呜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盖柳㮨者颇
与古之大贤穷理之法。其揆一也。而乃谓之罪人也。成浑之疏。明言讲学穷格之事。而谓之未尝言。用朱子语以陈于 天听。则谓之为道家者流。其言皆是以有为无。以无为有。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无非虚空中捏造言语。假立名字。以肆攻斥。无一言一字近实可信者。此真谗人罔极之情态。奸邪陷人之手段。舜所谓谗说殄行。孔子所谓利口覆邦者也。此非独诬先贤。其欺罔 圣明亦极矣。其罪不亦大矣乎。噫。此两臣生于偏邦绝学之中。一以古之圣贤为师。其学问德行。实可为百世师表。自吾东来不可多数。士林之尊仰。几至举国同然。岂非可敬可慕之人也。柳㮨乃敢肆然诋斥。略无顾忌。其曰。巧诋前辈。曲謢同己。号称经济而实务专擅。施措云为。偏蔽疏谬。又曰。好为躐等。未踏实地。蜃楼虚幻。既非吾儒家计。剥换面目。以济其说。又曰。其学专在气字。认气为理。其病元出陆家。又曰。落在儱侗科臼。又曰。偏见错认。又曰。朱子之罪人。其流祸馀烈。将不知其所税也。又曰。乃道家者流。非吾儒规模。学术颇僻。又曰。违伦伤教。乱道反经。其陵蔑践踏。肆其辱骂。至于此极。皆人所不忍闻不忍见。呜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盖柳㮨者颇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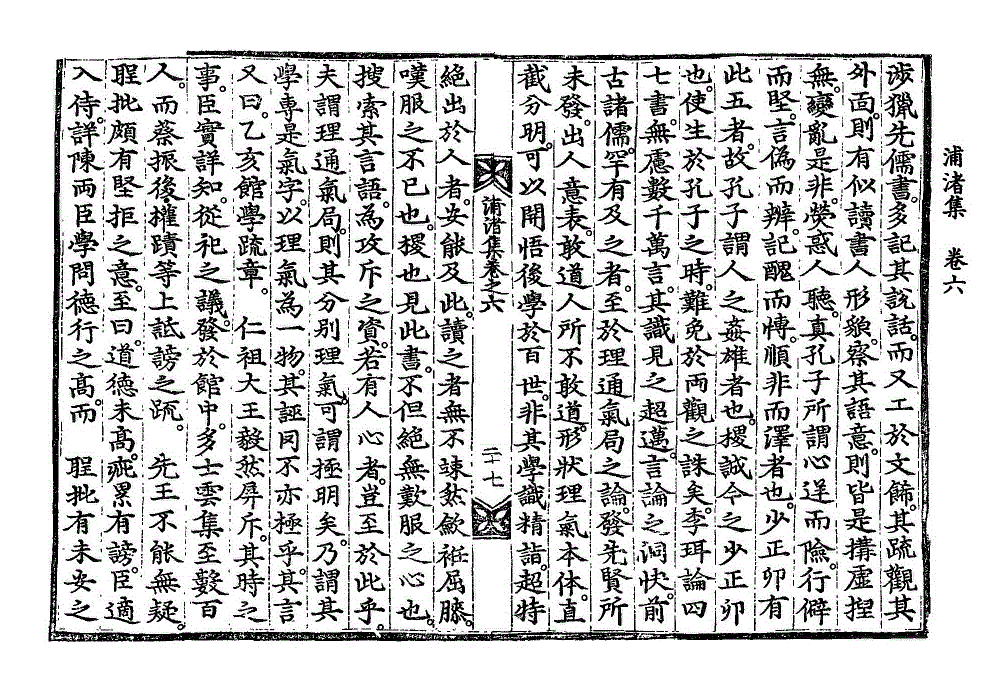 涉猎先儒书。多记其说话。而又工于文饰。其疏观其外面。则有似读书人形貌。察其语意。则皆是搆虚捏无。变乱是非。荧惑人听。真孔子所谓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者也。少正卯有此五者。故孔子谓人之奸雄者也。㮨诚今之少正卯也。使生于孔子之时。难免于两观之诛矣。李珥论四七书。无虑数千万言。其识见之超迈。言论之洞快。前古诸儒。罕有及之者。至于理通气局之论。发先贤所未发。出人意表。敢道人所不敢道。形状理气本体。直截分明。可以开悟后学于百世。非其学识精诣。超特绝出于人者。安能及此。读之者无不竦然敛衽屈膝。叹服之不已也。㮨也见此书。不但绝无叹服之心也。搜索其言语。为攻斥之资。若有人心者。岂至于此乎。夫谓理通气局。则其分别理气。可谓极明矣。乃谓其学专是气字。以理气为一物。其诬罔不亦极乎。其言又曰。乙亥馆学疏章。 仁祖大王毅然屏斥。其时之事。臣实详知。从祀之议。发于馆中。多士云集至数百人。而蔡振后,权迹等上诋谤之疏。 先王不能无疑。圣批颇有坚拒之意。至曰。道德未高。疵累有谤。臣适入侍。详陈两臣学问德行之高。而 圣批有未安之
涉猎先儒书。多记其说话。而又工于文饰。其疏观其外面。则有似读书人形貌。察其语意。则皆是搆虚捏无。变乱是非。荧惑人听。真孔子所谓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者也。少正卯有此五者。故孔子谓人之奸雄者也。㮨诚今之少正卯也。使生于孔子之时。难免于两观之诛矣。李珥论四七书。无虑数千万言。其识见之超迈。言论之洞快。前古诸儒。罕有及之者。至于理通气局之论。发先贤所未发。出人意表。敢道人所不敢道。形状理气本体。直截分明。可以开悟后学于百世。非其学识精诣。超特绝出于人者。安能及此。读之者无不竦然敛衽屈膝。叹服之不已也。㮨也见此书。不但绝无叹服之心也。搜索其言语。为攻斥之资。若有人心者。岂至于此乎。夫谓理通气局。则其分别理气。可谓极明矣。乃谓其学专是气字。以理气为一物。其诬罔不亦极乎。其言又曰。乙亥馆学疏章。 仁祖大王毅然屏斥。其时之事。臣实详知。从祀之议。发于馆中。多士云集至数百人。而蔡振后,权迹等上诋谤之疏。 先王不能无疑。圣批颇有坚拒之意。至曰。道德未高。疵累有谤。臣适入侍。详陈两臣学问德行之高。而 圣批有未安之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16L 页
 意。臣又曰。臣之此言。实非有一毫偏党之私。仍举臣曾前不为党之事而證之曰。今入侍者。东西南北皆在也。臣言若虚。则必有言其欺罔者也。 先王答曰。李珥极是善人。今时若有如此之人则极幸矣。又曰。吾非以其人道德不足。但以从祀事体极重。不敢轻易许之。自此日答儒生之疏。皆以温辞。更无不乐之语也。且两臣贤否。臣窃以为不难知也。当时陷李珥者。郑汝立也。陷成浑者。郑仁弘也。两臣门人著闻者。赵宪,金长生,吴允谦,李贵,黄慎等。其他行己有耻。居官廉洁者。及屏居田野。修身洁行而终焉者亦不少。自今观之。汝立,仁弘之言为是耶。赵宪,金长生等之言为是耶。至于今日。其敬服尊慕。几乎举国同然。而其憎嫉诟辱者。柳㮨等若干辈。举国同然之情为是耶。柳㮨等之言为是耶。盖柳㮨之论。即述汝立,仁弘之馀论也。然以李珥之学。为出于陆氏。以成浑之学。为道家者流。则虽汝立,仁弘。亦不敢为此言也。㮨也者其亦甚矣乎。以岭南一道言之。初则一道之论同然也。其后公论颇行。稍稍有开悟者。盖郑逑则常谓两臣为贤儒。张显光则尊慕无间然。郑经世。初则随其土俗。不免亦轻侮之。其后觉悟。常尊称之。臣亦亲
意。臣又曰。臣之此言。实非有一毫偏党之私。仍举臣曾前不为党之事而證之曰。今入侍者。东西南北皆在也。臣言若虚。则必有言其欺罔者也。 先王答曰。李珥极是善人。今时若有如此之人则极幸矣。又曰。吾非以其人道德不足。但以从祀事体极重。不敢轻易许之。自此日答儒生之疏。皆以温辞。更无不乐之语也。且两臣贤否。臣窃以为不难知也。当时陷李珥者。郑汝立也。陷成浑者。郑仁弘也。两臣门人著闻者。赵宪,金长生,吴允谦,李贵,黄慎等。其他行己有耻。居官廉洁者。及屏居田野。修身洁行而终焉者亦不少。自今观之。汝立,仁弘之言为是耶。赵宪,金长生等之言为是耶。至于今日。其敬服尊慕。几乎举国同然。而其憎嫉诟辱者。柳㮨等若干辈。举国同然之情为是耶。柳㮨等之言为是耶。盖柳㮨之论。即述汝立,仁弘之馀论也。然以李珥之学。为出于陆氏。以成浑之学。为道家者流。则虽汝立,仁弘。亦不敢为此言也。㮨也者其亦甚矣乎。以岭南一道言之。初则一道之论同然也。其后公论颇行。稍稍有开悟者。盖郑逑则常谓两臣为贤儒。张显光则尊慕无间然。郑经世。初则随其土俗。不免亦轻侮之。其后觉悟。常尊称之。臣亦亲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17H 页
 闻其尊之之语也。以此观之。则其中有贤名者。皆慕此两臣也。至于士子。知敬慕者亦甚多。夫秉彝之性。人皆有之。何独岭南有异也。特其迷溺之甚者犹不变也。顷日申硕亨等之事。实可嘉尚。身居岭南。而不染于乡习。闻先贤之风而慨然有慕。被黜乡黜道黜校削籍。侵虐百端。而硕亨等愤先贤之受侮。嫉邪说之诬人。不顾其祸。裹足远来。明其诬罔。其贤贤之诚。慕义之笃。真可谓无负于士之名也。臣于两臣。未及受业于其门。而窃从先生长者。闻其学问之正。德义之盛甚详且熟。其区区敬服之深。实无异于亲蒙教育也。今见奸人诟辱至此之极。窃不胜痛心伤骨。而仍又念邪说肆行。而莫之禁则其眩乱诖误。将至惑一世之人。其为祸岂下于洪水猛兽哉。然则息邪说放淫辞之责。非臣任之。谁肯任之哉。又念奸人谗搆之害。王政之所必禁也。谗害同时之人。其罪犹不可赦。况搆诬既往之先贤。罔有纪极。其计实欲上惑 天听。得以邪胜正也。 国家何可置之而不问乎。诚宜投畀有北。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也。臣窃不胜忧愤之至。敢陈愚虑。伏愿 圣明留神澄省焉。
闻其尊之之语也。以此观之。则其中有贤名者。皆慕此两臣也。至于士子。知敬慕者亦甚多。夫秉彝之性。人皆有之。何独岭南有异也。特其迷溺之甚者犹不变也。顷日申硕亨等之事。实可嘉尚。身居岭南。而不染于乡习。闻先贤之风而慨然有慕。被黜乡黜道黜校削籍。侵虐百端。而硕亨等愤先贤之受侮。嫉邪说之诬人。不顾其祸。裹足远来。明其诬罔。其贤贤之诚。慕义之笃。真可谓无负于士之名也。臣于两臣。未及受业于其门。而窃从先生长者。闻其学问之正。德义之盛甚详且熟。其区区敬服之深。实无异于亲蒙教育也。今见奸人诟辱至此之极。窃不胜痛心伤骨。而仍又念邪说肆行。而莫之禁则其眩乱诖误。将至惑一世之人。其为祸岂下于洪水猛兽哉。然则息邪说放淫辞之责。非臣任之。谁肯任之哉。又念奸人谗搆之害。王政之所必禁也。谗害同时之人。其罪犹不可赦。况搆诬既往之先贤。罔有纪极。其计实欲上惑 天听。得以邪胜正也。 国家何可置之而不问乎。诚宜投畀有北。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也。臣窃不胜忧愤之至。敢陈愚虑。伏愿 圣明留神澄省焉。劄论岭儒事后辞职疏
伏以臣于昨日。敢进劄陈其区区所怀。而臣素愚戆。
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17L 页
 思虑疏迂。言语朴拙。不能委曲从容。率多妄发。所上劄辞。徒知尽言无隐。不觉狂率支烦。反覆循省。惟窃悚惧。伏蒙 圣批矜其愚戆之甚。教以受病之多。有若慈父之教子。臣不胜羞愧震恐。继以感激也。臣之病痛。臣亦自知。深欲矫揉医治。庶几得免此病。而其区区所怀。终有不敢不别白者。敢复此略陈焉。夫柳㮨欺罔之奸。此固人情所共疾者。而岭儒废科之事。其欺罔又莫甚焉。岭儒若实欲废科。则何故远来京城及他道右道。且得出榜。此虽由都事善为开喻。而儒生等有废科之心。则何故赢粮备纸。来入场中。一闻开喻。从而制文乎。左道举子亦持纸打印入场。此非欲制者乎。由其不能开喻。而又有若干作变之徒受人风旨而煽动之。使不得制。诸生不敢不从而出耳。观此则其初所谓儒生皆不欲赴试者。岂非虚语乎。且闻监试初定之日。举子会两道试所者。各累千人。闻退定而归。其时状启。没其会者之多。而只言录名或八人或十人。此亦可怪也。此必有主谋之人欲禁制一道儒生。使皆不观试。而以诸生齐愤废科。上欺 天听。胁制 朝廷也。然而许多儒生。欲科之心。自不能禁。或来京。或往他道右道。则听开喻而制文。
思虑疏迂。言语朴拙。不能委曲从容。率多妄发。所上劄辞。徒知尽言无隐。不觉狂率支烦。反覆循省。惟窃悚惧。伏蒙 圣批矜其愚戆之甚。教以受病之多。有若慈父之教子。臣不胜羞愧震恐。继以感激也。臣之病痛。臣亦自知。深欲矫揉医治。庶几得免此病。而其区区所怀。终有不敢不别白者。敢复此略陈焉。夫柳㮨欺罔之奸。此固人情所共疾者。而岭儒废科之事。其欺罔又莫甚焉。岭儒若实欲废科。则何故远来京城及他道右道。且得出榜。此虽由都事善为开喻。而儒生等有废科之心。则何故赢粮备纸。来入场中。一闻开喻。从而制文乎。左道举子亦持纸打印入场。此非欲制者乎。由其不能开喻。而又有若干作变之徒受人风旨而煽动之。使不得制。诸生不敢不从而出耳。观此则其初所谓儒生皆不欲赴试者。岂非虚语乎。且闻监试初定之日。举子会两道试所者。各累千人。闻退定而归。其时状启。没其会者之多。而只言录名或八人或十人。此亦可怪也。此必有主谋之人欲禁制一道儒生。使皆不观试。而以诸生齐愤废科。上欺 天听。胁制 朝廷也。然而许多儒生。欲科之心。自不能禁。或来京。或往他道右道。则听开喻而制文。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18H 页
 于此可见儒生初不欲废科也。作为如此诪张。欲使圣明惧一道之离心。其为计亦可谓甚矣。臣区区恶恶之心。得于天性者。犹未丧失。故每见人有不正不直之事。则贱恶之心。不能自禁也。见此欺罔。心窃愤之。具劄欲上达久矣。以时未可而不敢进矣。昨因论北儒事。并及于此。而言辞鄙朴。失于委曲。务欲详陈。而不免过激。致勤 圣教。惶恐悚慄。无地自容。且臣愚陋无比。初无寸长。唯其平生区区立心。常欲以至公为心。 反正初。升平府院君金瑬,延平府院君李贵。俱以元勋。方主朝议。而其论或过当。则臣以小官。敢与之抗。务从公平。领议政李元翼及郑经世,李浚(一作埈)。皆所谓南人。而臣皆与之相亲。至于李元翼。则无异于骨肉。故常自谓无党也。及今见欺罔如此。安得不痛疾乎。今则谓臣为偏于为党可也。然前日之无党。今日之为党。其公心则一也。孔子曰。唯仁人。为能好人。能恶人。夫见人之恶而恶之。实理之正也。乃是公也仁也。若见恶而不恶。则失其心之正。乃不仁者也。臣虽至愚。其所好所恶。则亦或不敢不以正也。然臣之所言。则乃似偏于为党。 圣意在于调停。而臣则其偏如此。其不可用明矣。且其戆愚朴拙。言辄妄发。此
于此可见儒生初不欲废科也。作为如此诪张。欲使圣明惧一道之离心。其为计亦可谓甚矣。臣区区恶恶之心。得于天性者。犹未丧失。故每见人有不正不直之事。则贱恶之心。不能自禁也。见此欺罔。心窃愤之。具劄欲上达久矣。以时未可而不敢进矣。昨因论北儒事。并及于此。而言辞鄙朴。失于委曲。务欲详陈。而不免过激。致勤 圣教。惶恐悚慄。无地自容。且臣愚陋无比。初无寸长。唯其平生区区立心。常欲以至公为心。 反正初。升平府院君金瑬,延平府院君李贵。俱以元勋。方主朝议。而其论或过当。则臣以小官。敢与之抗。务从公平。领议政李元翼及郑经世,李浚(一作埈)。皆所谓南人。而臣皆与之相亲。至于李元翼。则无异于骨肉。故常自谓无党也。及今见欺罔如此。安得不痛疾乎。今则谓臣为偏于为党可也。然前日之无党。今日之为党。其公心则一也。孔子曰。唯仁人。为能好人。能恶人。夫见人之恶而恶之。实理之正也。乃是公也仁也。若见恶而不恶。则失其心之正。乃不仁者也。臣虽至愚。其所好所恶。则亦或不敢不以正也。然臣之所言。则乃似偏于为党。 圣意在于调停。而臣则其偏如此。其不可用明矣。且其戆愚朴拙。言辄妄发。此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18L 页
 亦由老妄而然也。臣以衰朽多病。忝窃大位。徒有尸素之羞。绝无丝毫之补。从前乞退久矣。其不可用又如此。何敢复此叨冒。以积罪戾。伏乞 圣明怜臣愚朴之甚。察臣无用之实。 亟命镌递。以便公私。不胜幸甚。臣无任兢惶愧忸战慄祈恳之至。
亦由老妄而然也。臣以衰朽多病。忝窃大位。徒有尸素之羞。绝无丝毫之补。从前乞退久矣。其不可用又如此。何敢复此叨冒。以积罪戾。伏乞 圣明怜臣愚朴之甚。察臣无用之实。 亟命镌递。以便公私。不胜幸甚。臣无任兢惶愧忸战慄祈恳之至。退归渡江时疏
伏以臣之才能无可取。百事不及人。无用于世。及其年纪颓暮。精神气力。皆已消耗。更无可为之状。臣之前后疏章。陈之已尽。而忝窃以来。一年有馀。迄无丝毫裨补。臣之自为愧怍。已知难容物议。讥诮又当如何。臣之陈情乞退不知其几。而未蒙 允许。又值 国家多事。不敢决然退去。僶勉就列。亦已久矣。今幸递免。庶可遂其所愿。谨具一疏。方拟仰渎 天听。而未及也。伏见岭南人疏。其辞专攻臣身。而 圣教以为其偏系不正。予已洞鉴。夫臣之不正。 圣教既已洞鉴。则臣之不可复容于世决矣。其羞愧悚慄。岂有其极。在臣私义。岂可一日安于都下。而又惶恐跼蹐。不敢仰辞于 阊阖之下。窃见古今人臣去国。或有不辞而行者。此盖出于不得已也。昨者伏蒙 特遣史臣。 恩谕甚勤。臣窃不胜感激惶悚。罔知所为。第
浦渚先生集卷之六 第 1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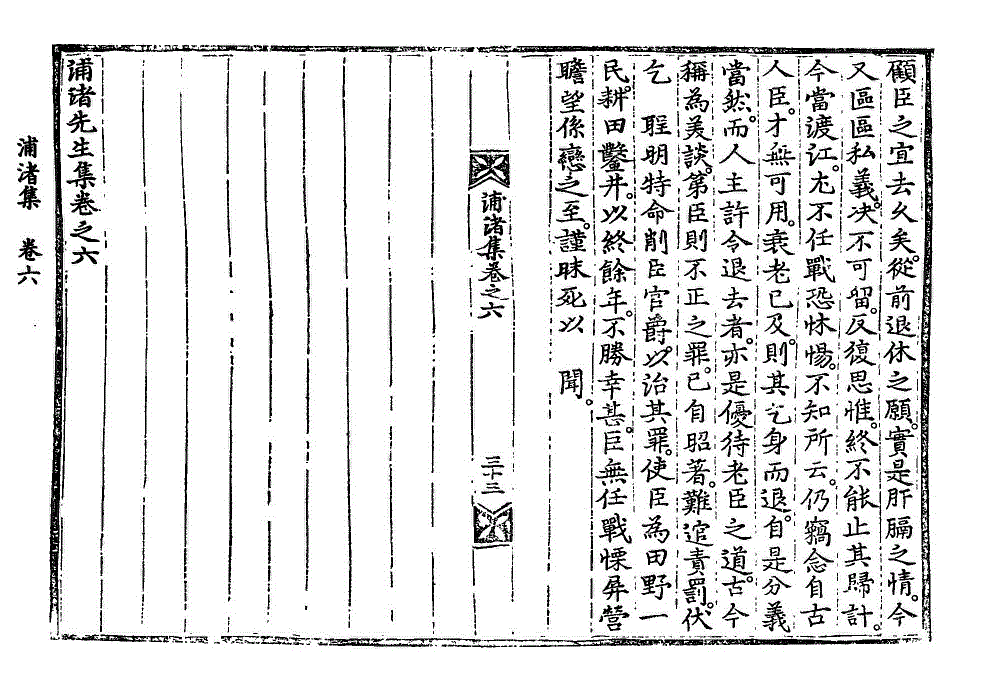 顾臣之宜去久矣。从前退休之愿。实是肝膈之情。今又区区私义。决不可留。反复思惟。终不能止其归计。今当渡江。尤不任战恐怵惕。不知所云。仍窃念自古人臣。才无可用。衰老已及。则其乞身而退。自是分义当然。而人主许令退去者。亦是优待老臣之道。古今称为美谈。第臣则不正之罪。已自昭著。难逭责罚。伏乞 圣明特命削臣官爵。以治其罪。使臣为田野一民。耕田凿井。以终馀年。不胜幸甚。臣无任战慄屏营瞻望系恋之至。谨昧死以 闻。
顾臣之宜去久矣。从前退休之愿。实是肝膈之情。今又区区私义。决不可留。反复思惟。终不能止其归计。今当渡江。尤不任战恐怵惕。不知所云。仍窃念自古人臣。才无可用。衰老已及。则其乞身而退。自是分义当然。而人主许令退去者。亦是优待老臣之道。古今称为美谈。第臣则不正之罪。已自昭著。难逭责罚。伏乞 圣明特命削臣官爵。以治其罪。使臣为田野一民。耕田凿井。以终馀年。不胜幸甚。臣无任战慄屏营瞻望系恋之至。谨昧死以 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