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x 页
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疏(十三首)
疏(十三首)
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88H 页
 论 王世子讲学疏(乙酉)
论 王世子讲学疏(乙酉)伏以 殿下计深 宗社。上顺天心。择立贤德。正位储贰。而 王世子仁闻远播。率土归心。兹蠲吉日。授以策命。缛仪斯举。天人胥悦。万物咸睹。和气欢声。盈溢区宇。斯岂非东方太平之基。而 国家万岁无疆之休也。而臣以老父昏耄疾病。不离枕席。日夜扶救。不忍暂离。无计趋诣 昕庭。以从诸臣之后。殚其蹈舞之诚。瞻望 宸极。心魂飞越。为恨为恐。不能为情。盖臣之老父。自今年三月以前。犹能起立行步。自四月以后。两脚全然无力。不能运动。尺寸之间。不能移身。须人举移。委废枕席。一日之内。坐者仅十之一。手不能执匙。饮食亦须人手。不能吃饭。只以粥饮度日。而所食至小。视此气力。朝夕莫保。其于人子冈极之情。为如何哉。以是。顷刻不敢离。咫尺不敢往。况敢往返数日之程乎。此臣之所以睹此大庆。不胜欢抃。而闷然退处。徒有悼恨者也。第窃伏惟念。 王世子既当储嗣之位。宜讲古昔圣贤之学。以圣贤之志为志。以圣贤所为之工夫为事。使其心志事为。一如古之
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88L 页
 帝王。此乃先儒所谓第一等也。切不可以第二等为心。以第二等事为事也。所谓圣贤之学者何也。臣谨按经传所载。圣人所言为学之方。唯舜禹授受危微精一之言。最为首出。而后来数千年群圣群贤之学。皆原于此也此言之义先儒解之详矣臣请复因先儒之说以明之也。盖一人之心。有人心焉。有道心焉。上智下愚。莫不皆有。而道心原于性命。而发为义理之正。人心根于形气。而发为一己之私。循乎道心者为善人。而其循也纯。则为圣为贤。循乎人心者为众人。而其循也纯。则为桀为蹠。凡天下古今为善为恶。只是分于此而已。道心虽所以为圣贤。非如声色之娱。利欲之诱。人所易喜。故苟非天质之美及有持养之力。则易至消亡。斯不亦微乎。人心即是私欲利害。苟无有以禁制。而恣其所至。则其为桀蹠不难矣。斯不亦危乎。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以相杂也。一则循乎义理之正。而不以间断也。此即所以禁制人心。持养道心之工夫也。如是则道心常为主于内。其发为言行。施为事业。无不一于义理之正。而人心之发。亦皆受其裁制。由乎涂辙。不得踰越以害道心。所谓允执厥中是也。夫一人之心。有所以为善者。有所以
帝王。此乃先儒所谓第一等也。切不可以第二等为心。以第二等事为事也。所谓圣贤之学者何也。臣谨按经传所载。圣人所言为学之方。唯舜禹授受危微精一之言。最为首出。而后来数千年群圣群贤之学。皆原于此也此言之义先儒解之详矣臣请复因先儒之说以明之也。盖一人之心。有人心焉。有道心焉。上智下愚。莫不皆有。而道心原于性命。而发为义理之正。人心根于形气。而发为一己之私。循乎道心者为善人。而其循也纯。则为圣为贤。循乎人心者为众人。而其循也纯。则为桀为蹠。凡天下古今为善为恶。只是分于此而已。道心虽所以为圣贤。非如声色之娱。利欲之诱。人所易喜。故苟非天质之美及有持养之力。则易至消亡。斯不亦微乎。人心即是私欲利害。苟无有以禁制。而恣其所至。则其为桀蹠不难矣。斯不亦危乎。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以相杂也。一则循乎义理之正。而不以间断也。此即所以禁制人心。持养道心之工夫也。如是则道心常为主于内。其发为言行。施为事业。无不一于义理之正。而人心之发。亦皆受其裁制。由乎涂辙。不得踰越以害道心。所谓允执厥中是也。夫一人之心。有所以为善者。有所以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89H 页
 为恶者。而为善者微而难保。为恶者危而易肆。若于此而不有以治之。任其微者自微。危者自危。则人人皆流而为恶。斯人为禽兽矣。故圣人于此。造为方法以治之。即惟精惟一是也。既察识二者美恶之殊。又为之裁制持养。使危者伏而听命。微者立而为主。尽此者为圣。守此者为贤。于是人道立。而可以参于天地矣。所谓圣贤之学。此其大纲也。此其渊源也。后来圣贤工夫。如孔子之博文约礼。曾子之格致诚正。子思,孟子之明善诚身。至于程朱子所谓居敬穷理。其要皆所以抑人心而立道心也。其事即皆精一两端工夫也。乃皆本于舜禹之旨。而千古一法也。圣贤之学。举其纲要。如是而已。所谓以圣贤之志为志者。凡天下之事业。以立志为先。必志之在先而后事从之。以人臣言之。则有志乎道德者。有志乎功名者。有志乎富贵者。以人君言之。则有志乎王者。有志乎伯者。有志乎从欲者。其人品之高下。事业之崇卑。无不由其志焉。圣贤之所以为圣贤。由其立心之初以如是之地位。如是之事业。自期于其心。故能为如是之工夫。以致如是之地位。如是之事业也。今于立志之初。能奋然以圣贤自期。如古圣贤当初所以立志者。即
为恶者。而为善者微而难保。为恶者危而易肆。若于此而不有以治之。任其微者自微。危者自危。则人人皆流而为恶。斯人为禽兽矣。故圣人于此。造为方法以治之。即惟精惟一是也。既察识二者美恶之殊。又为之裁制持养。使危者伏而听命。微者立而为主。尽此者为圣。守此者为贤。于是人道立。而可以参于天地矣。所谓圣贤之学。此其大纲也。此其渊源也。后来圣贤工夫。如孔子之博文约礼。曾子之格致诚正。子思,孟子之明善诚身。至于程朱子所谓居敬穷理。其要皆所以抑人心而立道心也。其事即皆精一两端工夫也。乃皆本于舜禹之旨。而千古一法也。圣贤之学。举其纲要。如是而已。所谓以圣贤之志为志者。凡天下之事业。以立志为先。必志之在先而后事从之。以人臣言之。则有志乎道德者。有志乎功名者。有志乎富贵者。以人君言之。则有志乎王者。有志乎伯者。有志乎从欲者。其人品之高下。事业之崇卑。无不由其志焉。圣贤之所以为圣贤。由其立心之初以如是之地位。如是之事业。自期于其心。故能为如是之工夫。以致如是之地位。如是之事业也。今于立志之初。能奋然以圣贤自期。如古圣贤当初所以立志者。即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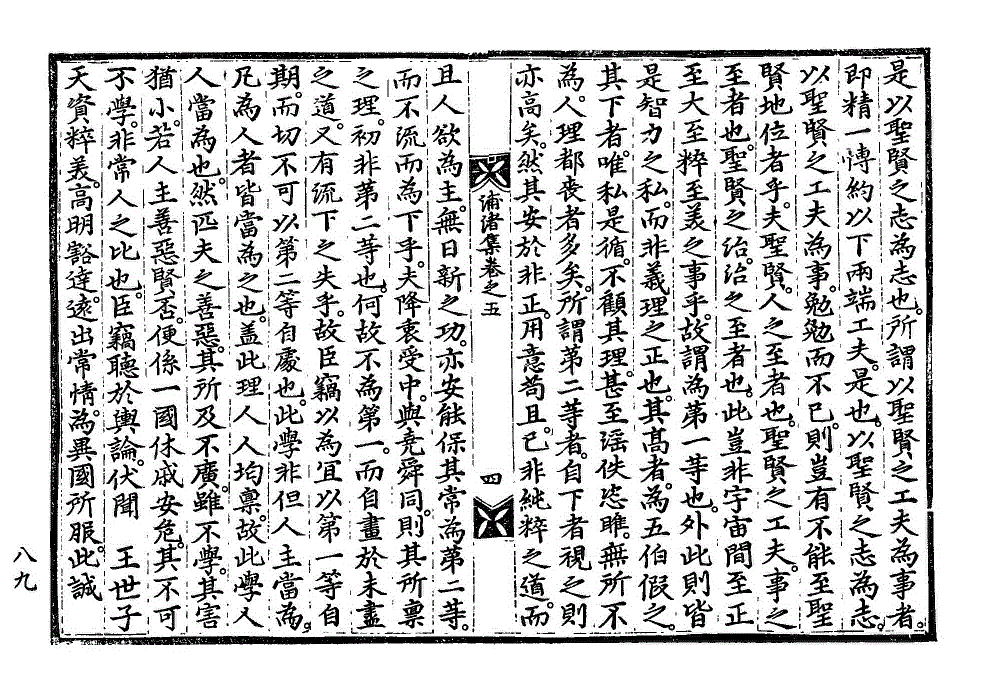 是以圣贤之志为志也。所谓以圣贤之工夫为事者。即精一博约以下两端工夫。是也。以圣贤之志为志。以圣贤之工夫为事。勉勉而不已。则岂有不能至圣贤地位者乎。夫圣贤。人之至者也。圣贤之工夫。事之至者也。圣贤之治。治之至者也。此岂非宇宙间至正至大至粹至美之事乎。故谓为第一等也。外此则皆是智力之私。而非义理之正也。其高者。为五伯假之。其下者。唯私是循。不顾其理。甚至淫佚恣睢。无所不为。人理都丧者多矣。所谓第二等者。自下者视之则亦高矣。然其安于非正。用意苟且。已非纯粹之道。而且人欲为主。无日新之功。亦安能保其常为第二等。而不流而为下乎。夫降衷受中。与尧舜同。则其所禀之理。初非第二等也。何故不为第一。而自画于未尽之道。又有流下之失乎。故臣窃以为宜以第一等自期。而切不可以第二等自处也。此学非但人主当为。凡为人者皆当为之也。盖此理人人均禀。故此学人人当为也。然匹夫之善恶。其所及不广。虽不学。其害犹小。若人主善恶贤否。便系一国休戚安危。其不可不学。非常人之比也。臣窃听于舆论。伏闻 王世子天资粹美。高明豁达。远出常情。为异国所服。此诚
是以圣贤之志为志也。所谓以圣贤之工夫为事者。即精一博约以下两端工夫。是也。以圣贤之志为志。以圣贤之工夫为事。勉勉而不已。则岂有不能至圣贤地位者乎。夫圣贤。人之至者也。圣贤之工夫。事之至者也。圣贤之治。治之至者也。此岂非宇宙间至正至大至粹至美之事乎。故谓为第一等也。外此则皆是智力之私。而非义理之正也。其高者。为五伯假之。其下者。唯私是循。不顾其理。甚至淫佚恣睢。无所不为。人理都丧者多矣。所谓第二等者。自下者视之则亦高矣。然其安于非正。用意苟且。已非纯粹之道。而且人欲为主。无日新之功。亦安能保其常为第二等。而不流而为下乎。夫降衷受中。与尧舜同。则其所禀之理。初非第二等也。何故不为第一。而自画于未尽之道。又有流下之失乎。故臣窃以为宜以第一等自期。而切不可以第二等自处也。此学非但人主当为。凡为人者皆当为之也。盖此理人人均禀。故此学人人当为也。然匹夫之善恶。其所及不广。虽不学。其害犹小。若人主善恶贤否。便系一国休戚安危。其不可不学。非常人之比也。臣窃听于舆论。伏闻 王世子天资粹美。高明豁达。远出常情。为异国所服。此诚 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90H 页
 宗社之福也。生民之福也。然臣窃恐其于圣贤之学。或未深讲也。夫圣贤之学。举其纲要而言之。则如惟精惟一。博文约礼。格致诚正。明善诚身等语固其要也。然其中有许多曲折工程。有学者终身勉勉而不能尽者。不可徒守其大纲而已也。圣贤遗训。具在方册。精一博约工夫。唯当就方册中深求其理而实践之也。以其次第言之。则四书为先。次及五经。又次及天下之书也。此非臣之臆说。程朱子教人之序如是也。夫四书为书。盈满世间。家家有之。凡为士者。谁不读之。故人皆视之为寻常浅近之语也。而不知天下之至理皆在于此。千载之下。欲求圣贤之心。唯于此得之。故程朱子教人。皆以此为先也。夫当时公卿大夫学士名流所与相从者。无非文义通达。记览该博者也。皆深劝此书。盖此等书。若泛然读过。不求其理。则虽尽诵其言。理实无得。与不读何异也。唯以求索其中义理为心。字字句句。精思密察。沈潜研究。反复咀嚼。久而不置。自然渐次融释。见解开通。中心悦怿。自有无穷之意味。不觉手舞而足蹈矣。如是则吾之知见。与圣贤知见吻然相合。方信圣贤所言皆吾所当行也。必于此等书。得如是之知解。而后其于圣门
宗社之福也。生民之福也。然臣窃恐其于圣贤之学。或未深讲也。夫圣贤之学。举其纲要而言之。则如惟精惟一。博文约礼。格致诚正。明善诚身等语固其要也。然其中有许多曲折工程。有学者终身勉勉而不能尽者。不可徒守其大纲而已也。圣贤遗训。具在方册。精一博约工夫。唯当就方册中深求其理而实践之也。以其次第言之。则四书为先。次及五经。又次及天下之书也。此非臣之臆说。程朱子教人之序如是也。夫四书为书。盈满世间。家家有之。凡为士者。谁不读之。故人皆视之为寻常浅近之语也。而不知天下之至理皆在于此。千载之下。欲求圣贤之心。唯于此得之。故程朱子教人。皆以此为先也。夫当时公卿大夫学士名流所与相从者。无非文义通达。记览该博者也。皆深劝此书。盖此等书。若泛然读过。不求其理。则虽尽诵其言。理实无得。与不读何异也。唯以求索其中义理为心。字字句句。精思密察。沈潜研究。反复咀嚼。久而不置。自然渐次融释。见解开通。中心悦怿。自有无穷之意味。不觉手舞而足蹈矣。如是则吾之知见。与圣贤知见吻然相合。方信圣贤所言皆吾所当行也。必于此等书。得如是之知解。而后其于圣门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90L 页
 之学。方得入头矣。伏惟 王世子聪明出类。春秋已壮。其于天下之书。必且无所不观矣。然臣窃愿且屈首俯躬于此等书。得此真正知见。直得置身于圣贤正路。而不落于第二等。以基东方他日尧舜之治也。窃念 王世子入处深宫之中。问安视膳之外。无耳目之烦。机务之扰。正是专精讲学之时也。若于此时不讲圣贤之学。不能办得圣贤心术田地。未免闲度时日。则岂非可惜可恨之甚也。故臣之区区狗马之诚。窃深有望焉。伏愿 殿下以此微臣所陈一得之愚。深劝勉之。而极选春坊进讲之官。不拘职秩高下及草野之人。苟有经学者。皆取之以备讲官之列。与之朝夕讲磨。如闾阎士人朋友讲习之事。则其裨益必多。而 王世子以聪明绝人之资。苟诚心求之。则亦必有不待人之启迪。而自能通透处多矣。昔孟子见他国之世子。言必称尧舜。况臣之区区贱诚。于 王世子。其愿为尧舜。岂有其极。安敢不以尧舜之道望之哉。且臣又窃有所愿焉。此懋学进德之功。乃千古圣贤用功之方也。不但宜以此劝勉 东宫。亦愿殿下加之意也。伏见 殿下临御日久。 天颜已非昔时。而臣之区区以此愿于 殿下者。昔成汤代夏
之学。方得入头矣。伏惟 王世子聪明出类。春秋已壮。其于天下之书。必且无所不观矣。然臣窃愿且屈首俯躬于此等书。得此真正知见。直得置身于圣贤正路。而不落于第二等。以基东方他日尧舜之治也。窃念 王世子入处深宫之中。问安视膳之外。无耳目之烦。机务之扰。正是专精讲学之时也。若于此时不讲圣贤之学。不能办得圣贤心术田地。未免闲度时日。则岂非可惜可恨之甚也。故臣之区区狗马之诚。窃深有望焉。伏愿 殿下以此微臣所陈一得之愚。深劝勉之。而极选春坊进讲之官。不拘职秩高下及草野之人。苟有经学者。皆取之以备讲官之列。与之朝夕讲磨。如闾阎士人朋友讲习之事。则其裨益必多。而 王世子以聪明绝人之资。苟诚心求之。则亦必有不待人之启迪。而自能通透处多矣。昔孟子见他国之世子。言必称尧舜。况臣之区区贱诚。于 王世子。其愿为尧舜。岂有其极。安敢不以尧舜之道望之哉。且臣又窃有所愿焉。此懋学进德之功。乃千古圣贤用功之方也。不但宜以此劝勉 东宫。亦愿殿下加之意也。伏见 殿下临御日久。 天颜已非昔时。而臣之区区以此愿于 殿下者。昔成汤代夏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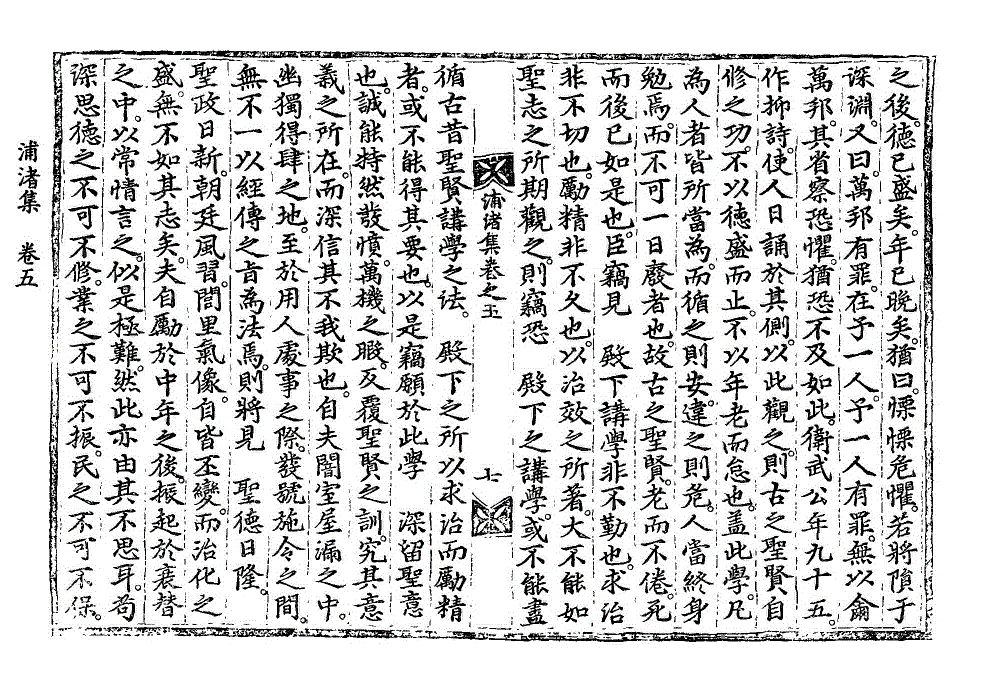 之后。德已盛矣。年已晚矣。犹曰。慄慄危惧。若将陨于深渊。又曰。万邦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邦。其省察恐惧。犹恐不及如此。卫武公年九十五。作抑诗。使人日诵于其侧。以此观之。则古之圣贤自修之功。不以德盛而止。不以年老而怠也。盖此学。凡为人者皆所当为。而循之则安。违之则危。人当终身勉焉。而不可一日废者也。故古之圣贤。老而不倦。死而后已如是也。臣窃见 殿下讲学非不勤也。求治非不切也。励精非不久也。以治效之所著。大不能如圣志之所期观之。则窃恐 殿下之讲学。或不能尽循古昔圣贤讲学之法。 殿下之所以求治而励精者。或不能得其要也。以是窃愿于此学 深留圣意也。诚能特然发愤。万机之暇。反覆圣贤之训。究其意义之所在。而深信其不我欺也。自夫闇室屋漏之中。幽独得肆之地。至于用人处事之际。发号施令之间。无不一以经传之旨为法焉。则将见 圣德日隆。 圣政日新。朝廷风习。闾里气像。自皆丕变。而治化之盛。无不如其志矣。夫自励于中年之后。振起于衰替之中。以常情言之。似是极难。然此亦由其不思耳。苟深思德之不可不修。业之不可不振。民之不可不保。
之后。德已盛矣。年已晚矣。犹曰。慄慄危惧。若将陨于深渊。又曰。万邦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邦。其省察恐惧。犹恐不及如此。卫武公年九十五。作抑诗。使人日诵于其侧。以此观之。则古之圣贤自修之功。不以德盛而止。不以年老而怠也。盖此学。凡为人者皆所当为。而循之则安。违之则危。人当终身勉焉。而不可一日废者也。故古之圣贤。老而不倦。死而后已如是也。臣窃见 殿下讲学非不勤也。求治非不切也。励精非不久也。以治效之所著。大不能如圣志之所期观之。则窃恐 殿下之讲学。或不能尽循古昔圣贤讲学之法。 殿下之所以求治而励精者。或不能得其要也。以是窃愿于此学 深留圣意也。诚能特然发愤。万机之暇。反覆圣贤之训。究其意义之所在。而深信其不我欺也。自夫闇室屋漏之中。幽独得肆之地。至于用人处事之际。发号施令之间。无不一以经传之旨为法焉。则将见 圣德日隆。 圣政日新。朝廷风习。闾里气像。自皆丕变。而治化之盛。无不如其志矣。夫自励于中年之后。振起于衰替之中。以常情言之。似是极难。然此亦由其不思耳。苟深思德之不可不修。业之不可不振。民之不可不保。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91L 页
 则其忧勤惕厉。自不能已矣。亦何难之有哉。古人以责难于君为敬。臣安敢不以难事望于 殿下。而谓吾君不能哉。臣于昔日。以懋学之说。仰尘 天听亦屡矣。是时臣所学至浅。其言安能发明 圣学之要。而动 圣明之听乎。且有诸己而后求诸人。于敌以下尚然。其身尚不能以儒者绳墨自律。安能仰裨 圣德之万一乎。宜其不概于 圣心也。至今思之。窃不胜愧恨也。今臣复以此说进。臣之庸虚无识。固犹夫前也。然其言或不害为可绩。若不以人废言。而 少垂察焉。则岂惟愚臣幸甚。 宗社幸甚。亿兆幸甚。臣扶侍亲病。气息奄奄。忧惶罔极。百事无心。而唯是区区爱 君忧世之念。不敢忘于怀也。敢陈其肝血之诚。仰冀万一之补。伏愿 圣明矜其愚而察其忱。不胜幸甚。
则其忧勤惕厉。自不能已矣。亦何难之有哉。古人以责难于君为敬。臣安敢不以难事望于 殿下。而谓吾君不能哉。臣于昔日。以懋学之说。仰尘 天听亦屡矣。是时臣所学至浅。其言安能发明 圣学之要。而动 圣明之听乎。且有诸己而后求诸人。于敌以下尚然。其身尚不能以儒者绳墨自律。安能仰裨 圣德之万一乎。宜其不概于 圣心也。至今思之。窃不胜愧恨也。今臣复以此说进。臣之庸虚无识。固犹夫前也。然其言或不害为可绩。若不以人废言。而 少垂察焉。则岂惟愚臣幸甚。 宗社幸甚。亿兆幸甚。臣扶侍亲病。气息奄奄。忧惶罔极。百事无心。而唯是区区爱 君忧世之念。不敢忘于怀也。敢陈其肝血之诚。仰冀万一之补。伏愿 圣明矜其愚而察其忱。不胜幸甚。辞礼曹判书疏
伏以昨者。礼曹下人来传今月十二日政。伏蒙 天恩除臣为礼曹判书者。臣闻 命惊惶。罔知攸措。臣之老父病重。不得暂离之意。前疏已尽陈达矣。盖其病非如一时感伤所致。可以时月而期其差复者。乃耄老已甚。气力精神。日渐消耗。今则全不能运动。日
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92H 页
 夜委废枕席。起居饮食。皆须人手。已过半年。不能吃饭。以粥饮度日。而所食至少。视听全然昏迷。一室之内。不能辨形声。观此气力。朝夕莫保。亲病至此。其于人子之情。罔极为如何哉。况可忍而离去乎。此非但孝子知其不可离。虽不孝之人。亦知其不可离矣。非但士类知其不可离。虽奴隶下贱。亦知其不可离矣。非但举朝之所共知。举国之人。凡知臣者皆知之矣。不谓 天眷至隆。乃收取草野之臣。授以宗伯之重。臣仰感 鸿私。衷情自激。虽縻粉不足上报。而情势若此。不得趋诣 阙下。以谢 恩命。惶恐震掉。罪死难赎。且非但今也。臣父缕命尚在之日。臣身决不可弃去。古人所谓事亲日短。事君日长者。真可谓实获我心也。臣之情事。不亦可悲乎。臣非高尚之人也。亦非但自求安逸也。只为亲病危重。不忍离去耳。诚众人之所共怜悯也。伏愿 圣明天地父母。怜臣情事如此。亟 命递臣新授之职。无使天职久旷。而使臣得扶救亲病于穷山蓬荜之中。以终馀日。不胜幸甚。
夜委废枕席。起居饮食。皆须人手。已过半年。不能吃饭。以粥饮度日。而所食至少。视听全然昏迷。一室之内。不能辨形声。观此气力。朝夕莫保。亲病至此。其于人子之情。罔极为如何哉。况可忍而离去乎。此非但孝子知其不可离。虽不孝之人。亦知其不可离矣。非但士类知其不可离。虽奴隶下贱。亦知其不可离矣。非但举朝之所共知。举国之人。凡知臣者皆知之矣。不谓 天眷至隆。乃收取草野之臣。授以宗伯之重。臣仰感 鸿私。衷情自激。虽縻粉不足上报。而情势若此。不得趋诣 阙下。以谢 恩命。惶恐震掉。罪死难赎。且非但今也。臣父缕命尚在之日。臣身决不可弃去。古人所谓事亲日短。事君日长者。真可谓实获我心也。臣之情事。不亦可悲乎。臣非高尚之人也。亦非但自求安逸也。只为亲病危重。不忍离去耳。诚众人之所共怜悯也。伏愿 圣明天地父母。怜臣情事如此。亟 命递臣新授之职。无使天职久旷。而使臣得扶救亲病于穷山蓬荜之中。以终馀日。不胜幸甚。辞 世子左宾客,司䆃提调疏。
伏以臣于顷者。伏蒙 天恩。猥忝非分之职。感激 恩宠。灭身难报。而第顾九十奄奄。不能运动之老亲。
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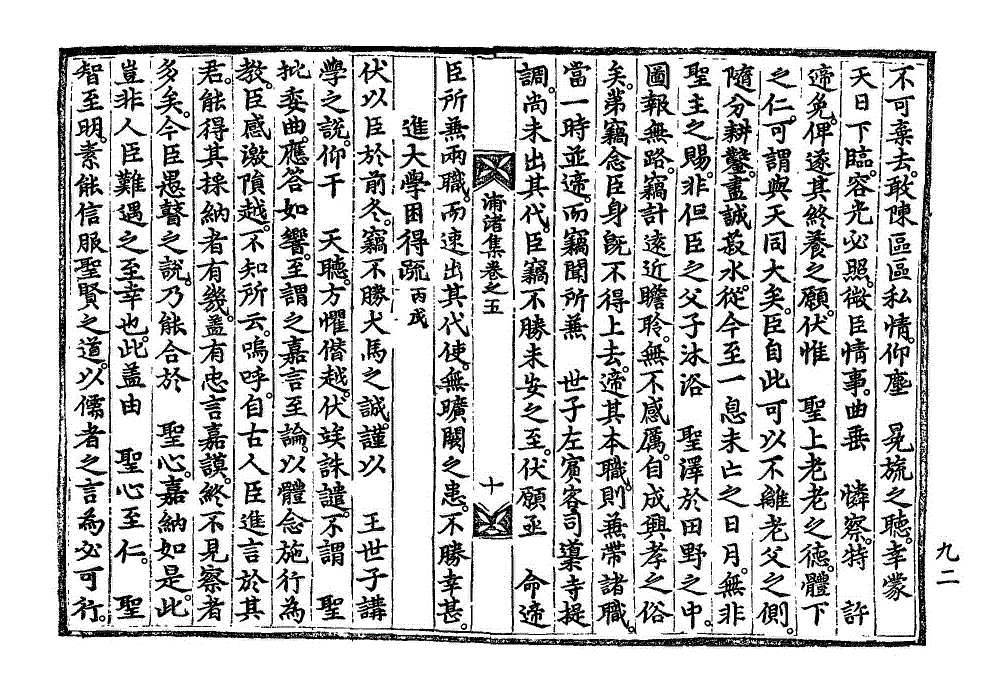 不可弃去。敢陈区区私情。仰尘 冕旒之听。幸蒙 天日下临。容光必照。微臣情事。曲垂 怜察。特 许递免。俾遂其终养之愿。伏惟 圣上老老之德。体下之仁。可谓与天同大矣。臣自此可以不离老父之侧。随分耕凿。尽诚菽水。从今至一息未亡之日月。无非圣主之赐。非但臣之父子沐浴 圣泽于田野之中。图报无路。窃计远近瞻聆。无不感厉。自成兴孝之俗矣。第窃念臣身既不得上去。递其本职。则兼带诸职。当一时并递。而窃闻所兼 世子左宾客,司䆃寺提调。尚未出其代。臣窃不胜未安之至。伏愿亟 命递臣所兼两职。而速出其代使。无旷阙之患。不胜幸甚。
不可弃去。敢陈区区私情。仰尘 冕旒之听。幸蒙 天日下临。容光必照。微臣情事。曲垂 怜察。特 许递免。俾遂其终养之愿。伏惟 圣上老老之德。体下之仁。可谓与天同大矣。臣自此可以不离老父之侧。随分耕凿。尽诚菽水。从今至一息未亡之日月。无非圣主之赐。非但臣之父子沐浴 圣泽于田野之中。图报无路。窃计远近瞻聆。无不感厉。自成兴孝之俗矣。第窃念臣身既不得上去。递其本职。则兼带诸职。当一时并递。而窃闻所兼 世子左宾客,司䆃寺提调。尚未出其代。臣窃不胜未安之至。伏愿亟 命递臣所兼两职。而速出其代使。无旷阙之患。不胜幸甚。进大学困得疏(丙戌)
伏以臣于前冬。窃不胜犬马之诚。谨以 王世子讲学之说。仰干 天听。方惧僭越。伏俟诛谴。不谓 圣批委曲。应答如响。至谓之嘉言至论。以体念施行为教。臣感激陨越。不知所云。呜呼。自古人臣进言于其君。能得其采纳者有几。盖有忠言嘉谟。终不见察者多矣。今臣愚瞽之说。乃能合于 圣心。嘉纳如是。此岂非人臣难遇之至幸也。此盖由 圣心至仁。 圣智至明。素能信服圣贤之道。以儒者之言为必可行。
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93H 页
 故一闻愚臣拾掇先儒绪馀之论。便以为可用。信之而不疑。此 殿下重道之诚。听言之明。实前代人主所不能及。而臣之所言。非臣之言也。乃皆本于先儒之旨也。则使其说得行。未必不为 宗社生灵之幸也。然则臣之进此言。 殿下之喜闻之也。安知其非东方太平之一机会也。呜呼臣之妄论。既蒙 察纳。苟更有可以丝毫裨补者。敢不益殚愚虑。罄竭底蕴。罗列而进乎。臣谨按天下之书至精至粹至正至要。自书典谟诸篇。诗大雅颂诸什之外。未有如四书者也。然三王以前。世代高远。文辞简约。圣人言行。所传者甚略。至孔孟。其言与事。可详而见也。而其与门人弟子反复论难。亲切明白。今读之。无异面命耳受。而其一言一字。无非至道精义也。故千古圣贤可师可法。未有如孔孟者也。夫孔孟为万世之师法。则孔孟之书。岂不为万世学者之常业乎。后之人欲学圣人。非学孔孟而何。欲学孔孟。非由四书而何也。故四书者。万世学圣人之正业也。臣窃考汉时文字。未见有并称论孟者。至唐韩柳之文。有云论语,孟子书。宋之文人论文章。以论孟为法。然未知由是以学圣人也。至程子。始以此为学问大法。盖自孟子后学绝。天下
故一闻愚臣拾掇先儒绪馀之论。便以为可用。信之而不疑。此 殿下重道之诚。听言之明。实前代人主所不能及。而臣之所言。非臣之言也。乃皆本于先儒之旨也。则使其说得行。未必不为 宗社生灵之幸也。然则臣之进此言。 殿下之喜闻之也。安知其非东方太平之一机会也。呜呼臣之妄论。既蒙 察纳。苟更有可以丝毫裨补者。敢不益殚愚虑。罄竭底蕴。罗列而进乎。臣谨按天下之书至精至粹至正至要。自书典谟诸篇。诗大雅颂诸什之外。未有如四书者也。然三王以前。世代高远。文辞简约。圣人言行。所传者甚略。至孔孟。其言与事。可详而见也。而其与门人弟子反复论难。亲切明白。今读之。无异面命耳受。而其一言一字。无非至道精义也。故千古圣贤可师可法。未有如孔孟者也。夫孔孟为万世之师法。则孔孟之书。岂不为万世学者之常业乎。后之人欲学圣人。非学孔孟而何。欲学孔孟。非由四书而何也。故四书者。万世学圣人之正业也。臣窃考汉时文字。未见有并称论孟者。至唐韩柳之文。有云论语,孟子书。宋之文人论文章。以论孟为法。然未知由是以学圣人也。至程子。始以此为学问大法。盖自孟子后学绝。天下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93L 页
 之士不知圣人之可学。未有以学圣人为志者。至程子。始知以孔孟为学。而学孔孟之道。在于孔孟之书也。故以此二书。深究力索。得之于己。而又解释之。以教门人。又取庸学二篇于戴记中。合以为四。庸学亦孔门之书也。盖于天下之书。择其至精至粹至正至要者。只得此四件书也。朱子之学。得之于程氏之传。非但以是教门人。当时执友老成之人。虽至公卿达官者。亦皆以是劝之。而著为集注章句。以明其义。自是。四书之旨粲如日星。垂之万世。人之为道。坦若大路。苟由是而求之。无不可至圣贤之域者矣。先贤继往开来之功。岂不大哉。先贤立定功程。开创门户。以教天下后世若是其明白。而后之人鲜复有留意于此者。可胜叹哉。然则臣之前疏所谓 王世子宜以圣贤之志为志。以圣贤之学为事。以期至于圣贤之域。而用功以四书为先者。岂臣之臆说也。实皆先贤之旨也。臣又按程朱子以四书为教。而又皆以大学为先也。盖此书内外本末兼备。功程节次分明。一篇之中。该尽学问始终工夫先后。其读而致精。不过旬月之功。而其所思而得之者。内而心术之微。外而天下之广。近而顷刻之间。久而终身之远。荡然全体之
之士不知圣人之可学。未有以学圣人为志者。至程子。始知以孔孟为学。而学孔孟之道。在于孔孟之书也。故以此二书。深究力索。得之于己。而又解释之。以教门人。又取庸学二篇于戴记中。合以为四。庸学亦孔门之书也。盖于天下之书。择其至精至粹至正至要者。只得此四件书也。朱子之学。得之于程氏之传。非但以是教门人。当时执友老成之人。虽至公卿达官者。亦皆以是劝之。而著为集注章句。以明其义。自是。四书之旨粲如日星。垂之万世。人之为道。坦若大路。苟由是而求之。无不可至圣贤之域者矣。先贤继往开来之功。岂不大哉。先贤立定功程。开创门户。以教天下后世若是其明白。而后之人鲜复有留意于此者。可胜叹哉。然则臣之前疏所谓 王世子宜以圣贤之志为志。以圣贤之学为事。以期至于圣贤之域。而用功以四书为先者。岂臣之臆说也。实皆先贤之旨也。臣又按程朱子以四书为教。而又皆以大学为先也。盖此书内外本末兼备。功程节次分明。一篇之中。该尽学问始终工夫先后。其读而致精。不过旬月之功。而其所思而得之者。内而心术之微。外而天下之广。近而顷刻之间。久而终身之远。荡然全体之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94H 页
 大。森然节目之详。无不毕备。而圣贤事业。皆昭然见其可力致也。苟于此得其滋味。则自然欲罢而不能矣。此先儒所以先之也。臣窃愿 王世子且先从事于此书也。且臣之读此书。今五十年矣。始者因章句求之。至于沈潜积年。忽然若得其微意。辄用自喜。录之为说。虽自知僭妄之极。亦疑或得其彷佛也。曾于甲子年。见 经筵讲此等书。妄意或万一有补。敢冒昧上进。其后观之。见其乖谬颇多。又丛杂无可取。至今为愧惕也。十许年来。潜伏穷山。得究心于旧业。因复修削。或似不至大乖经旨。今于 王世子讲学之日。敢妄陈一得之愚。乃幸蒙 开纳如此。在臣微诚。何敢有所隐匿。兹谨将前所僭著大学困得一卷。缮写封进。若此区区管窥。或丝毫有补于 王世子研索之功。则其幸孰大。而亦窃愿 殿下于乙夜之闲。或一览过。则亦恐未必无丝毫之补也。臣今年六十有八。馀年几何。而臣父八十九岁。自前年夏月以后。全不能运动。坐卧须人。视听全然昏迷。不辨声形。委身枕席。萎薾日甚。臣日夜侍侧。顷刻不得离。唯有一向忧闷。绝无毫发他念。唯窃以 王世子今日讲学。所关极重。敢复以此区区僭妄之说。仰尘 睿览。惶
大。森然节目之详。无不毕备。而圣贤事业。皆昭然见其可力致也。苟于此得其滋味。则自然欲罢而不能矣。此先儒所以先之也。臣窃愿 王世子且先从事于此书也。且臣之读此书。今五十年矣。始者因章句求之。至于沈潜积年。忽然若得其微意。辄用自喜。录之为说。虽自知僭妄之极。亦疑或得其彷佛也。曾于甲子年。见 经筵讲此等书。妄意或万一有补。敢冒昧上进。其后观之。见其乖谬颇多。又丛杂无可取。至今为愧惕也。十许年来。潜伏穷山。得究心于旧业。因复修削。或似不至大乖经旨。今于 王世子讲学之日。敢妄陈一得之愚。乃幸蒙 开纳如此。在臣微诚。何敢有所隐匿。兹谨将前所僭著大学困得一卷。缮写封进。若此区区管窥。或丝毫有补于 王世子研索之功。则其幸孰大。而亦窃愿 殿下于乙夜之闲。或一览过。则亦恐未必无丝毫之补也。臣今年六十有八。馀年几何。而臣父八十九岁。自前年夏月以后。全不能运动。坐卧须人。视听全然昏迷。不辨声形。委身枕席。萎薾日甚。臣日夜侍侧。顷刻不得离。唯有一向忧闷。绝无毫发他念。唯窃以 王世子今日讲学。所关极重。敢复以此区区僭妄之说。仰尘 睿览。惶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94L 页
 恐悚惕。若无所容焉。
恐悚惕。若无所容焉。辞吏曹判书疏
伏以本月初三日。吏曹下人持政目官教来示臣。乃于初一日政除臣为吏曹判书者。臣承 命震惧。罔知攸措。夫冢宰之职。主进退一世人物之权。朝路之清浊。众职之修废。皆在于冢宰之贤否。实一世治乱安危所系。其任之重。为如何哉。故必得一时贤人君子。藻鉴极其精明。好恶极其公正者。乃可以授此职也。臣之愚陋。最在诸臣之下。虽庶官之微。尚恐不能尽其当然。以无负任使之责。况此天官莫重之职哉。臣自知其不能。审矣。 殿下虽误而任臣。臣安敢误而受任。以伤 圣上知人之明。以累 圣朝任人之道哉。臣之不敢当此职固决矣。且臣窃有区区私情。实不堪其闷迫者。臣曾以不忍离去老父之意。仰渎天听。非止一再。臣之情事。 殿下固已洞烛矣。今敢复略陈焉。臣父今年八十九岁。世间年龄。到此者实极少也。其气力之微弱。精神之昏耗。理之所必然者也。臣父自前年初夏以后。两脚全然无力。不能起立。坐卧亦不能自由。皆须人扶。尺寸之地。不能迁移。心神昏迷。一家子孙奴婢。亦不能记其名。目不能视。耳
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95H 页
 不能听。唯有气息微如一缕。疾病又易作。往往而剧。则便至不省人事。食饮专废。累日而后乃差。如此者比比焉。观此气力。朝夕不可保。此岂人子一刻可离之时乎。以是。自前年以前或时滥蒙 恩命。至京拜谢。或省丘墓于畿甸。离亲或数日或一旬者。一年或一二焉。自前年夏月老父不能运动之后。实未尝一日离去也。盖暂时离侧。非但臣心所不忍。老父尤不忍焉。忆念甚苦。岂可使耄年缕命。奄奄至弱。常时不可保朝夕之老亲。复有相离忆念之苦乎。盖人子之慕其亲。人亲之思其子。老少顿异。若父母不甚年高。气力强健。则虽相离至累年。犹能堪过。世之游仕远方。久而不得还者何限。人亦视之为常事也。至于衰老之后。则非但人子不忍离其亲。亲心亦恋恋不忍焉。以是。先王之制。亲年七十。不授外任三百里外者。其酌量父子之情。可谓曲尽矣。此先王体群臣之美意也。七十犹不可远离。况九十乎。今臣若贪冒 恩宠。忍而离去。翩然上去。勤于供仕。则其区区闷迫之情。虽不敢说。其于人理如何。其于不孝之恶如何。人之视之如何哉。窃恐 圣明亦视之为非人也。昔叶公诸梁之弟后臧。自吴弃母而归。诸梁终不正视。今
不能听。唯有气息微如一缕。疾病又易作。往往而剧。则便至不省人事。食饮专废。累日而后乃差。如此者比比焉。观此气力。朝夕不可保。此岂人子一刻可离之时乎。以是。自前年以前或时滥蒙 恩命。至京拜谢。或省丘墓于畿甸。离亲或数日或一旬者。一年或一二焉。自前年夏月老父不能运动之后。实未尝一日离去也。盖暂时离侧。非但臣心所不忍。老父尤不忍焉。忆念甚苦。岂可使耄年缕命。奄奄至弱。常时不可保朝夕之老亲。复有相离忆念之苦乎。盖人子之慕其亲。人亲之思其子。老少顿异。若父母不甚年高。气力强健。则虽相离至累年。犹能堪过。世之游仕远方。久而不得还者何限。人亦视之为常事也。至于衰老之后。则非但人子不忍离其亲。亲心亦恋恋不忍焉。以是。先王之制。亲年七十。不授外任三百里外者。其酌量父子之情。可谓曲尽矣。此先王体群臣之美意也。七十犹不可远离。况九十乎。今臣若贪冒 恩宠。忍而离去。翩然上去。勤于供仕。则其区区闷迫之情。虽不敢说。其于人理如何。其于不孝之恶如何。人之视之如何哉。窃恐 圣明亦视之为非人也。昔叶公诸梁之弟后臧。自吴弃母而归。诸梁终不正视。今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95L 页
 臣弃父而进。则人岂有正视者乎。今虽只谢 恩而归。往返当至旬日。臣父气力。朝夕不可保。况旬日之间。安能保其安过乎。使其苦忆旬日。则生疾必矣。生疾则能救何可必乎。臣之决不可进。窃恐举世之人皆知其必然也。伏愿 圣明天地父母。察臣情事如此。亦察人理当然。亟 命递臣新授之职。使臣不离老父之侧。得区区致力于菽水之奉。以终其馀命。则非但臣之父子殒结难报。其于 圣上孝理之政。体群臣之道。无所不尽。非但一世之所观仰。将永为后代之美法矣。
臣弃父而进。则人岂有正视者乎。今虽只谢 恩而归。往返当至旬日。臣父气力。朝夕不可保。况旬日之间。安能保其安过乎。使其苦忆旬日。则生疾必矣。生疾则能救何可必乎。臣之决不可进。窃恐举世之人皆知其必然也。伏愿 圣明天地父母。察臣情事如此。亦察人理当然。亟 命递臣新授之职。使臣不离老父之侧。得区区致力于菽水之奉。以终其馀命。则非但臣之父子殒结难报。其于 圣上孝理之政。体群臣之道。无所不尽。非但一世之所观仰。将永为后代之美法矣。辞左参赞疏(戊子)
伏以臣于前月二十七日。伏奉二十三日所下有 旨。以臣为议政府左参赞。令臣乘驲上来者。臣即于私舍祗受讫。惊惶震掉。措躬无所。窃念臣罪衅交积。祸殃极酷。老父于丙戌之夏。奄尔违背。终天之痛。无所逮及。顽命犹存。三年驷过。孤露天地。若无所依。不谓丧制初除。 恩擢遽加。 召命远下。至于给马之命。又是殊异之 恩数。臣本庸愚。无足比数。乃此非常之 宠。岂素望所敢及。顾已推分。感激涕零。继以悚慄。即宜促装裹足。颠倒上道。走诣 龙庭。仰谢
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96H 页
 天宠。而臣穷命薄福。惨祸连仍。乃于季夏。又失第四子进士来阳。臣性本柔弱。过于慈爱。唯自径情摧割。不知保惜躯命。因得腹痛泄泻之证。有时刺痛。若不可堪。今至月馀。百药无效。臣以七十之年。才经草土。又此惨痛。其气之伤败。固无足怪。而苦痛踰月。羸惫日甚。委身枕席。食饮顿废。暂时触冷。痛辄增剧。且秋节过半。日气渐寒。以此气力。以此病患。强起登途。决非所堪。私窃闷迫。罔知所为。以是趑趄累日。计无所出。窃伏念臣事君。犹子事父。父子之间。何所不可言。兹敢以病苦闷迫之情。仰达于 冕旒之下。伏愿 圣明天地父母。特垂哀怜。亟 命还收所授新 命。使臣得安意穷庐。以专调治。庶微命获全于 仁覆之下。不胜幸甚。
天宠。而臣穷命薄福。惨祸连仍。乃于季夏。又失第四子进士来阳。臣性本柔弱。过于慈爱。唯自径情摧割。不知保惜躯命。因得腹痛泄泻之证。有时刺痛。若不可堪。今至月馀。百药无效。臣以七十之年。才经草土。又此惨痛。其气之伤败。固无足怪。而苦痛踰月。羸惫日甚。委身枕席。食饮顿废。暂时触冷。痛辄增剧。且秋节过半。日气渐寒。以此气力。以此病患。强起登途。决非所堪。私窃闷迫。罔知所为。以是趑趄累日。计无所出。窃伏念臣事君。犹子事父。父子之间。何所不可言。兹敢以病苦闷迫之情。仰达于 冕旒之下。伏愿 圣明天地父母。特垂哀怜。亟 命还收所授新 命。使臣得安意穷庐。以专调治。庶微命获全于 仁覆之下。不胜幸甚。乞致仕疏
伏以七十致仕。礼经定制。盖先王参酌人生老少盛衰之限。以为之制。著之于经。垂之万世。此岂非凡人所当遵守之大法也。然人之禀气。强弱不同。或有虽过七十而坚悍如壮年者。如此则不必以礼经为拘也。亦有残病之人未老先衰。昏耗如笃老者。此则不待年至。而便可退休也。然先王所定人生老少之限。
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96L 页
 众人之所同然也。其或先衰或后衰者。是其禀气异于众人。世所稀罕也。夫未老而先衰者。犹当退休。况其衰病已甚。而年又已至者乎。窃念臣罪负极重。赋命极险。至于衰晚之年。连遭惨酷之丧。自壬午以后。死亡相继。稚孙壮子忽然逝去者非一二。而至于丙戌。则丧亲丧妻。又丧长子。一年之内。重丧三出。世间凶祸。岂有如臣之酷者乎。今年又丧一子一孙。天之降殃。何至此极乎。七年之间。长以忧煎。伤痛哭泣。衰麻素蔬度日。夫迟暮之年。虽使居处饮食好美。心虑安闲。善自颐养。岁月荏苒。衰谢自不能禁。况其戕害斲丧如是者乎。虽使受气完厚之人。遭此患苦。其摧败毁伤。自不能免。况臣气禀微弱。在众人尤甚者乎。臣以至弱之质。沈没于祸患酷烈之中。积有年数。其气力之毁败。精神之耗失。固无足怪。其可怪者。惟未死耳。其伤败如此。虽未至于衰老。犹不可用也。况臣犬马之齿已至七十。正是礼经致仕之年。其宜退休。以情势礼制。皆所当然也。兹者伏蒙 圣慈不遗旧物。才免草土。收置显列。 恩召远及草野。臣感激无任。而适贱疾方苦。敢陈疏乞免。不谓 天眷极隆。不忍遽弃。 恩命再下。令其调理上来。尤切感惕。不敢
众人之所同然也。其或先衰或后衰者。是其禀气异于众人。世所稀罕也。夫未老而先衰者。犹当退休。况其衰病已甚。而年又已至者乎。窃念臣罪负极重。赋命极险。至于衰晚之年。连遭惨酷之丧。自壬午以后。死亡相继。稚孙壮子忽然逝去者非一二。而至于丙戌。则丧亲丧妻。又丧长子。一年之内。重丧三出。世间凶祸。岂有如臣之酷者乎。今年又丧一子一孙。天之降殃。何至此极乎。七年之间。长以忧煎。伤痛哭泣。衰麻素蔬度日。夫迟暮之年。虽使居处饮食好美。心虑安闲。善自颐养。岁月荏苒。衰谢自不能禁。况其戕害斲丧如是者乎。虽使受气完厚之人。遭此患苦。其摧败毁伤。自不能免。况臣气禀微弱。在众人尤甚者乎。臣以至弱之质。沈没于祸患酷烈之中。积有年数。其气力之毁败。精神之耗失。固无足怪。其可怪者。惟未死耳。其伤败如此。虽未至于衰老。犹不可用也。况臣犬马之齿已至七十。正是礼经致仕之年。其宜退休。以情势礼制。皆所当然也。兹者伏蒙 圣慈不遗旧物。才免草土。收置显列。 恩召远及草野。臣感激无任。而适贱疾方苦。敢陈疏乞免。不谓 天眷极隆。不忍遽弃。 恩命再下。令其调理上来。尤切感惕。不敢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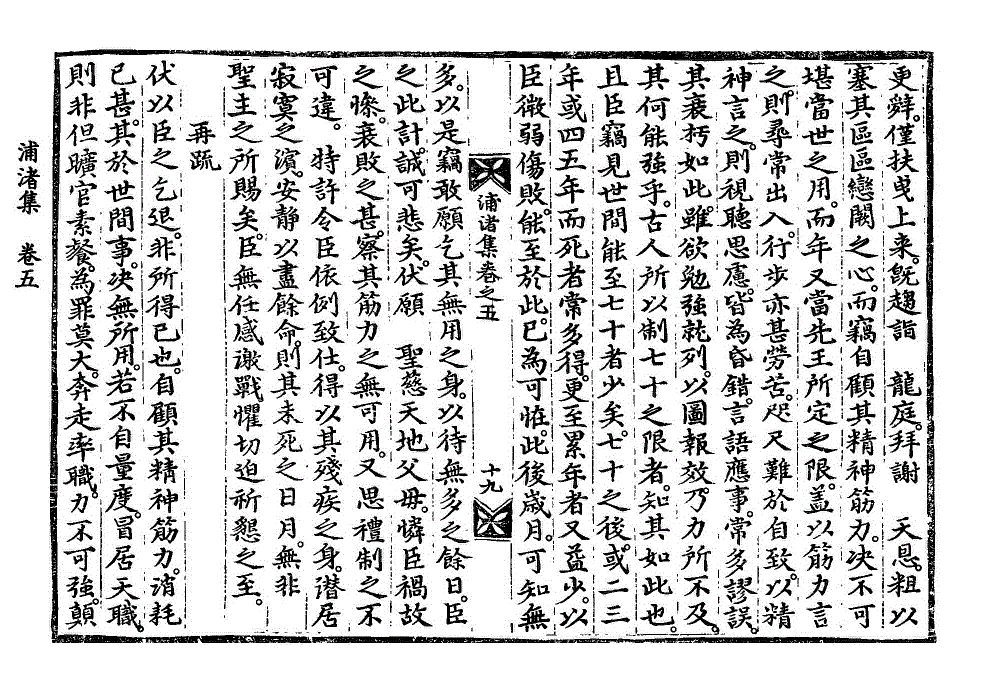 更辞。仅扶曳上来。既趋诣 龙庭。拜谢 天恩。粗以塞其区区恋阙之心。而窃自顾其精神筋力。决不可堪当世之用。而年又当先王所定之限。盖以筋力言之。则寻常出入。行步亦甚劳苦。咫尺难于自致。以精神言之。则视听思虑。皆为昏错。言语应事。常多谬误。其衰朽如此。虽欲勉强就列。以图报效。乃力所不及。其何能强乎。古人所以制七十之限者。知其如此也。且臣窃见世间能至七十者少矣。七十之后。或二三年或四五年而死者常多得。更至累年者又益少。以臣微弱伤败。能至于此。已为可怪。此后岁月。可知无多。以是窃敢愿乞其无用之身。以待无多之馀日。臣之此计。诚可悲矣。伏愿 圣慈天地父母。怜臣祸故之惨。衰败之甚。察其筋力之无可用。又思礼制之不可违。 特许令臣依例致仕。得以其残疾之身。潜居寂寞之滨。安静以尽馀命。则其未死之日月。无非 圣主之所赐矣。臣无任感激战惧切迫祈恳之至。
更辞。仅扶曳上来。既趋诣 龙庭。拜谢 天恩。粗以塞其区区恋阙之心。而窃自顾其精神筋力。决不可堪当世之用。而年又当先王所定之限。盖以筋力言之。则寻常出入。行步亦甚劳苦。咫尺难于自致。以精神言之。则视听思虑。皆为昏错。言语应事。常多谬误。其衰朽如此。虽欲勉强就列。以图报效。乃力所不及。其何能强乎。古人所以制七十之限者。知其如此也。且臣窃见世间能至七十者少矣。七十之后。或二三年或四五年而死者常多得。更至累年者又益少。以臣微弱伤败。能至于此。已为可怪。此后岁月。可知无多。以是窃敢愿乞其无用之身。以待无多之馀日。臣之此计。诚可悲矣。伏愿 圣慈天地父母。怜臣祸故之惨。衰败之甚。察其筋力之无可用。又思礼制之不可违。 特许令臣依例致仕。得以其残疾之身。潜居寂寞之滨。安静以尽馀命。则其未死之日月。无非 圣主之所赐矣。臣无任感激战惧切迫祈恳之至。乞致仕疏[再疏]
伏以臣之乞退。非所得已也。自顾其精神筋力。消耗已甚。其于世间事。决无所用。若不自量度。冒居天职。则非但旷官素餐。为罪莫大。奔走率职。力不可强。颠
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97L 页
 仆必矣。且计其馀日无多。朝夕不可保。唯有退去田野。安于穷约。待尽馀日。是其所宜。故敢控沥仰吁。冀蒙 矜察。伏承 圣批曰。危急之秋。非致仕之时。臣惶恐蹜踖。罔知攸措。呜呼。今之时可谓危且急矣。 朝廷之上。未见雍穆之美。闾里之间。不胜怨咨之多。天灾物怪。式月斯生。将来之忧。有不可胜言。诚可为痛哭流涕者矣。 圣教所谓危急者。实深见可忧之形而有此 教也。主忧臣辱。 圣教及此。凡在臣工。孰不感涕。然危急之时。其进退有关者。乃其才可以扶颠持危。缓急有用之人也。如臣衰朽昏谬。万无可用者。岂一毫有关于时乎。臣之积年悲伤。残败昏妄之情。前疏所陈。皆是实状。非敢一毫虚妄。其遭此丧祸。实人所未有也。其残败如此。亦人所未有也。既有此人所未有之丧祸。则其有此人所未有之残败。实理所必然。此无非臣得罪神明以致之。而其残败既如此。则其无所用。可知也。凡人之为事。只是用气力也。用精神也。气力如此。精神如此。则其所以为事者亡矣。何事能为乎。臣眼昏耳聋。灯下不得见文字。对人言语。太半不能解听。心虑昏错。所虑事谬误者。十常八九。凡所思量。或至半而忽忘之。或已思而旋失
仆必矣。且计其馀日无多。朝夕不可保。唯有退去田野。安于穷约。待尽馀日。是其所宜。故敢控沥仰吁。冀蒙 矜察。伏承 圣批曰。危急之秋。非致仕之时。臣惶恐蹜踖。罔知攸措。呜呼。今之时可谓危且急矣。 朝廷之上。未见雍穆之美。闾里之间。不胜怨咨之多。天灾物怪。式月斯生。将来之忧。有不可胜言。诚可为痛哭流涕者矣。 圣教所谓危急者。实深见可忧之形而有此 教也。主忧臣辱。 圣教及此。凡在臣工。孰不感涕。然危急之时。其进退有关者。乃其才可以扶颠持危。缓急有用之人也。如臣衰朽昏谬。万无可用者。岂一毫有关于时乎。臣之积年悲伤。残败昏妄之情。前疏所陈。皆是实状。非敢一毫虚妄。其遭此丧祸。实人所未有也。其残败如此。亦人所未有也。既有此人所未有之丧祸。则其有此人所未有之残败。实理所必然。此无非臣得罪神明以致之。而其残败既如此。则其无所用。可知也。凡人之为事。只是用气力也。用精神也。气力如此。精神如此。则其所以为事者亡矣。何事能为乎。臣眼昏耳聋。灯下不得见文字。对人言语。太半不能解听。心虑昏错。所虑事谬误者。十常八九。凡所思量。或至半而忽忘之。或已思而旋失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98H 页
 之。如此者常多。不知此由年老而然也。抑恐哀伤之久。心神有伤而然也。以是臣自分为无用之物。不敢比数于人也。其区区哀恳。非但愿以其衰病之身。安过垂尽之日月。实恐妄受决不可堪之职事。旷官败事而为罪也。伏愿 圣慈天地父母。怜臣残疾如此。特 允其所愿。使无用之物。安于无用之分。以终其馀日。不胜幸甚。臣无任瞻天望 圣祈恳战惧之至。
之。如此者常多。不知此由年老而然也。抑恐哀伤之久。心神有伤而然也。以是臣自分为无用之物。不敢比数于人也。其区区哀恳。非但愿以其衰病之身。安过垂尽之日月。实恐妄受决不可堪之职事。旷官败事而为罪也。伏愿 圣慈天地父母。怜臣残疾如此。特 允其所愿。使无用之物。安于无用之分。以终其馀日。不胜幸甚。臣无任瞻天望 圣祈恳战惧之至。乞致仕疏[三疏]
伏以臣以衰病不敢任职事。再陈疏章。愿乞骸骨。而圣批慇勤。不许其去。臣伏切感激悚惧。罔知所为。窃念臣之无状。何足为有无。只以其忝窃之旧。 圣意眷怜如是耳。臣虽至愚。宁不知感。其区区犬马之心。亦不忍于永诀尧舜。嘿嘿尸位。不敢更言去。今月馀日矣。第自顾精神筋力。决不可堪任使。若感激 恩宠。受任而不辞。则其旷阙天职。堕坏国事。上负 圣明。下愧素心。为罪莫大。臣虽不敢自爱。亦何敢坐受罪戾。臣窃百尔思惟。与其闷嘿受任。以取瘝旷偾事之罪。宁冒昧烦渎。更陈其无用之实。以冀 察纳。臣之衰病之实。前疏已尽陈之。盖筋骸气力。残败困劣。固衰境常事。唯是健忘之病最甚。凡朝暮间所闻所
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98L 页
 为。皆旋即忘失。茫然不复记忆。此则衰暮之人所皆然也。凡国家大小职任。皆有规例。皆有利害。必有所审察。有所计度。乃能无失其宜。不至败事。其昏忘如是。则何能审察。何能计度。则何事能为。何事不败。此臣之所以恐惧退缩。而决不敢当职任者也。盖七十之年。凡人盛衰之大数也。故古人致仕。以此为定限。到此而不衰者。实甚罕也。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朱子解之曰。孔子盛时。志欲行周公之道。故梦寐之间。如或见之。及其老而衰也。则无复是心。而无复是梦也。盖孔子七十三而卒。此语恐在七十间也。夫以圣人忧世之心。行道之志。常汲汲焉。及其气力已衰。无复可为。则亦无是心也。盖其心虽不能忘世。其如力不可为何哉。窃念臣之庸愚朴拙。最在人下。其于壮年。固绝无可用之才。然其心则于当世之治乱。亦常窃致思焉。至或有妄论得失之时矣。虽其言不足采。而其愿忠之心。则亦不可谓无矣。二三年以来。气血精神。顿觉消耗。况又积年悲哀惨痛。摧割心肠。到今健忘昏错。如前所陈。已成一无用之人。且自顾身世悲凉。馀日无多。万事皆已灰心。无复一毫世念久矣。今虽欲作起已灰之心。勉出已
为。皆旋即忘失。茫然不复记忆。此则衰暮之人所皆然也。凡国家大小职任。皆有规例。皆有利害。必有所审察。有所计度。乃能无失其宜。不至败事。其昏忘如是。则何能审察。何能计度。则何事能为。何事不败。此臣之所以恐惧退缩。而决不敢当职任者也。盖七十之年。凡人盛衰之大数也。故古人致仕。以此为定限。到此而不衰者。实甚罕也。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朱子解之曰。孔子盛时。志欲行周公之道。故梦寐之间。如或见之。及其老而衰也。则无复是心。而无复是梦也。盖孔子七十三而卒。此语恐在七十间也。夫以圣人忧世之心。行道之志。常汲汲焉。及其气力已衰。无复可为。则亦无是心也。盖其心虽不能忘世。其如力不可为何哉。窃念臣之庸愚朴拙。最在人下。其于壮年。固绝无可用之才。然其心则于当世之治乱。亦常窃致思焉。至或有妄论得失之时矣。虽其言不足采。而其愿忠之心。则亦不可谓无矣。二三年以来。气血精神。顿觉消耗。况又积年悲哀惨痛。摧割心肠。到今健忘昏错。如前所陈。已成一无用之人。且自顾身世悲凉。馀日无多。万事皆已灰心。无复一毫世念久矣。今虽欲作起已灰之心。勉出已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99H 页
 消之气。以周旋于世事。何可能乎。故其区区私计。只愿其身得弃遗。不当事任。为世闲人。以待死日而已。且臣窃见前史。人臣告老而归者前后相望。夫君之于臣。视犹一体。其眷顾之恩。待遇之厚。岂欲其去哉。然皆从而许之者。盖其筋力已不可用。而其休退之愿。出于至情。乃其身之切计也。故人主不忍强违之也。皆许其去。实所以加惠老臣也。乃人主之美事也。伏愿 圣明天地父母。察臣无用之实。谅臣肝血之诚。 特允其所愿。使得免于瘝旷之罪。息其筋骨之劳。屏居闲寂之地。安其疏粝之分。以终其无多之馀日。则从今至死。无非感 恩之日月矣。臣无任激切祈恳之至。
消之气。以周旋于世事。何可能乎。故其区区私计。只愿其身得弃遗。不当事任。为世闲人。以待死日而已。且臣窃见前史。人臣告老而归者前后相望。夫君之于臣。视犹一体。其眷顾之恩。待遇之厚。岂欲其去哉。然皆从而许之者。盖其筋力已不可用。而其休退之愿。出于至情。乃其身之切计也。故人主不忍强违之也。皆许其去。实所以加惠老臣也。乃人主之美事也。伏愿 圣明天地父母。察臣无用之实。谅臣肝血之诚。 特允其所愿。使得免于瘝旷之罪。息其筋骨之劳。屏居闲寂之地。安其疏粝之分。以终其无多之馀日。则从今至死。无非感 恩之日月矣。臣无任激切祈恳之至。乞扫坟疏
伏以臣母坟在广州。而臣将父就食湖西。始者。每年一再归省丘墓。及父病沈绵。长在床褥。则不得一日暂离。而罪殃极重。终至不救。草土之中。又不敢远去几筵。至于三年才毕。又遭惨丧。则摧割方深。不暇及于省墓。及承 召上来。又不敢枉道过松楸。其惨祸连仍。无非得罪于天以致之。而不得省母坟。今五六年矣。烈烈之痛。常切心腑。而到今不省丘墓如是之
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99L 页
 久。不孝之罪。至此尤大。区区伤痛。生不如死也。今者正岁又近。哀慕之情。益不能自禁。其愿归省丘陇。实是罔极之至情。而其往还之间。不出于一旬之内矣。伏愿 圣慈曲谅微臣切迫之情。 特许往来展省。使得遂其情愿。不胜幸甚。
久。不孝之罪。至此尤大。区区伤痛。生不如死也。今者正岁又近。哀慕之情。益不能自禁。其愿归省丘陇。实是罔极之至情。而其往还之间。不出于一旬之内矣。伏愿 圣慈曲谅微臣切迫之情。 特许往来展省。使得遂其情愿。不胜幸甚。进论孟浅说疏(己丑)
伏以圣人。人伦之极也。凡人无贵贱大小。皆当仰而取法焉者也。三代以上圣人。则世代既远。文籍残缺。其言与事。不可得而详焉。其世代差后。其言与事。可得详而学焉者。唯孔孟是也。然则孔孟岂非万世之所当师法者乎。孔孟之言与事可得而详焉者。唯在论孟二书。然则此二书者。岂非万世之所当法式焉者乎。臣愚窃以为圣人。人之至者也。此二书。书之至者也。人之欲为善者。不在于他求。只于此二书。读之思之反复之而不已焉而已。诚能于此二书。熟读精思。使其自首至尾。其言其意。无精与粗。一一了了分明。无毫发疑晦处。则其知识通透。自能知道义之可乐。而凡世间他事。皆见其无可留情者矣。如是而其处心行事。又一一以此二书之言为法。使其所为皆不离于圣贤规矩绳墨之内。则斯为善人。斯为君子。
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100H 页
 斯为圣贤矣。然则学问之道。岂在远求。岂是难为乎。故臣愚窃以为此二书。人当终身读之者也。人君终身读之。则无不为圣君。人臣终身读之。则无不为贤臣矣。臣之愚陋。最在人下。其于百事。无有能及人者。独幸自少偶因读书。见圣贤之言而悦之。因得以究心焉。读之愈久。而愈见其有味。盖读而味之者。今五十年馀矣。以其用力之专。岁月之久。不无解晓处。虽不敢自是。然此皆积年辛勤咀嚼所得。终亦未见其于经意大有差谬。故区区窃自喜。恐其忘也。因又窃录之。积成卷秩。此臣愚一生区区迂拙之事业也。近者窃闻 王世子书筵进讲。方以此书。此正得其当务之急者。而 王世子问难之语。皆其书中深意所在处。于此臣窃窥 王世子所讲。非惟读诵其言。又欲求其意义。诚能于此两书。深求其意而洞然无不通达。则其识见之明。德行之进。不可为限量。而其为宗社生民之福。又何可胜言哉。臣窃不胜区区欣庆之至。因窃伏念。臣之区区贱业。虽不足观。然农马之专。或未必无一得之愚。于圣贤微意。或不无丝毫发明。而于 王世子研究之功。亦或不无丝毫裨补。如或果有万一之补。则岂独微臣之幸。实 宗社生民
斯为圣贤矣。然则学问之道。岂在远求。岂是难为乎。故臣愚窃以为此二书。人当终身读之者也。人君终身读之。则无不为圣君。人臣终身读之。则无不为贤臣矣。臣之愚陋。最在人下。其于百事。无有能及人者。独幸自少偶因读书。见圣贤之言而悦之。因得以究心焉。读之愈久。而愈见其有味。盖读而味之者。今五十年馀矣。以其用力之专。岁月之久。不无解晓处。虽不敢自是。然此皆积年辛勤咀嚼所得。终亦未见其于经意大有差谬。故区区窃自喜。恐其忘也。因又窃录之。积成卷秩。此臣愚一生区区迂拙之事业也。近者窃闻 王世子书筵进讲。方以此书。此正得其当务之急者。而 王世子问难之语。皆其书中深意所在处。于此臣窃窥 王世子所讲。非惟读诵其言。又欲求其意义。诚能于此两书。深求其意而洞然无不通达。则其识见之明。德行之进。不可为限量。而其为宗社生民之福。又何可胜言哉。臣窃不胜区区欣庆之至。因窃伏念。臣之区区贱业。虽不足观。然农马之专。或未必无一得之愚。于圣贤微意。或不无丝毫发明。而于 王世子研究之功。亦或不无丝毫裨补。如或果有万一之补。则岂独微臣之幸。实 宗社生民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100L 页
 之大幸也。于是而若不以此上进。则是负其平生区区事国之诚。岂其心之所敢安哉。兹敢冒昧呈进。仰冀 王世子从容反复之际。幸一赐观览。而亦窃伏冀 圣明于万机之暇。乙夜之间。亦或赐观焉。则亦恐或不无丝毫之补也。且曾借人以写。其写不精。又多追改添书挟书处。而急于仰渎。未及改写。因此奉进。不胜惶恐之至。臣无任瞻天望 圣战惧祈望之至。谨昧死以 闻。
之大幸也。于是而若不以此上进。则是负其平生区区事国之诚。岂其心之所敢安哉。兹敢冒昧呈进。仰冀 王世子从容反复之际。幸一赐观览。而亦窃伏冀 圣明于万机之暇。乙夜之间。亦或赐观焉。则亦恐或不无丝毫之补也。且曾借人以写。其写不精。又多追改添书挟书处。而急于仰渎。未及改写。因此奉进。不胜惶恐之至。臣无任瞻天望 圣战惧祈望之至。谨昧死以 闻。请 抑哀调摄疏
伏以臣衰谢之气力。昧于调摄之宜。因致疾病之侵。沈绵委顿。今一月有馀矣。当此 谅闇哀毁之日。诸臣遑遑忧闷。奔走候问于 阙下。而臣乃退伏私室。独抱区区疾恙。不能强起就列。私窃惶闷。罪合万死。不谓 圣恩天大。不以为罪。反加矜怜。至 遣医临视。 赐以药物。臣感激惶惕。无地自容。惟思糜粉无以仰报。而臣气血凋耗。根本微弱。疾病易乘。离却甚难。调治日久。大势似减。馀症尚在。呻吟犹苦。昨者伏闻 内殿症候卒然增剧。至于夜里召医。臣不胜惊闷。不敢退卧。即力疾谢 恩。而因往来劳动。症势益苦重。四体之劳倦。胸膈之烦闷。比前尤甚。委废枕席。
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101H 页
 私窃闷扰。不意都宪之 命。乃及于卧病之时。决不能勉强萎薾。旅进随行。以供职事。而沈痼已久。差歇难期。台宪之长。岂容如臣衰朽之人抱疾冒居。以取瘝旷之罪哉。伏愿 圣明特怜微臣残病如此。 亟赐镌改。使专意调病。不胜幸甚。因窃伏念。亲丧。人之所必自致者也。先王因人心之所不能自已者。而为之礼法。庐室之次。衰麻之数。饮食之节。日月之限。皆为之定制。所谓称情而立文。是也。盖其至痛在心。故其居处饮食凡所以奉身者。皆极其粗恶。以称其情也。此非但使不及者企而及之。亦为贤者防其过也。又虑夫人以血肉之身。当此粗恶之极。生病者必多。故云有疾则饮酒食肉。又云毁瘠为病。君子不为也。又云毁不灭性。又云无以死伤生。如此之语。又丁宁反复。不一而足也。盖人子至痛之情。不可不使之自尽也。故制为粗恶之极。以称其情。而若一任其自尽。而不为裁节。则其生病必矣。生病之后。不为之变通。则其伤生必矣。夫人子之丧其亲。尽其哀痛。虽至情之所必然者。而至于过毁而致伤。则其为害莫大。父母惟疾之忧。则其心岂欲其如是哉。此则虽曰尽于孝。而反有伤于孝也。伏惟 殿下圣孝出天。自 侍
私窃闷扰。不意都宪之 命。乃及于卧病之时。决不能勉强萎薾。旅进随行。以供职事。而沈痼已久。差歇难期。台宪之长。岂容如臣衰朽之人抱疾冒居。以取瘝旷之罪哉。伏愿 圣明特怜微臣残病如此。 亟赐镌改。使专意调病。不胜幸甚。因窃伏念。亲丧。人之所必自致者也。先王因人心之所不能自已者。而为之礼法。庐室之次。衰麻之数。饮食之节。日月之限。皆为之定制。所谓称情而立文。是也。盖其至痛在心。故其居处饮食凡所以奉身者。皆极其粗恶。以称其情也。此非但使不及者企而及之。亦为贤者防其过也。又虑夫人以血肉之身。当此粗恶之极。生病者必多。故云有疾则饮酒食肉。又云毁瘠为病。君子不为也。又云毁不灭性。又云无以死伤生。如此之语。又丁宁反复。不一而足也。盖人子至痛之情。不可不使之自尽也。故制为粗恶之极。以称其情。而若一任其自尽。而不为裁节。则其生病必矣。生病之后。不为之变通。则其伤生必矣。夫人子之丧其亲。尽其哀痛。虽至情之所必然者。而至于过毁而致伤。则其为害莫大。父母惟疾之忧。则其心岂欲其如是哉。此则虽曰尽于孝。而反有伤于孝也。伏惟 殿下圣孝出天。自 侍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101L 页
 汤之日。及夫 宾天之始。致忧致哀。无所不至。至今庐居极其卑狭。衰绖不去乎体。哭泣之戚。深墨之色。虽闾阎匹夫善于居丧者。亦不能过也。自古人君能行三年丧者亦少。惟晋武帝,元魏孝文及宋孝宗。以孝闻于后世。然其哀戚之至。则未必皆及于 殿下也。伏惟 殿下之至行。诚卓冠于前古。而可传于百代也。然臣民之心。虽莫不感服。而亦莫不忧恐。盖恐其 心神之伤损。气力之消减。积以日月。今虽无形见之疾病。将来之忧。岂不甚大。且凡人之气体强弱。以贵贱而不同。虽士大夫尊贵之人。与草野寒贱者迥异。况至尊之身。其居养与闾阎匹夫万万殊绝者乎。今以 至尊之居养。为闾阎匹夫之哀毁。其伤损岂不大可惧哉。且人主一身。为皇天 宗庙之所付畀。为亿兆生灵之所仰戴。必能尽于修己治人之道。使朝廷清明。民生乂安。无有一民不得其所者。跻斯世于隆古。延国祚于无疆。此人主之大孝也。然则人主一身。其重如何。诚宜慎于自保。勿致伤损。岂可比匹夫私行。徒以致于哀毁为孝乎。又况古人著居丧之节曰。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忧。盖悲哀之心。以日月杀也。自遭 大戚。今已三月矣。古人不
汤之日。及夫 宾天之始。致忧致哀。无所不至。至今庐居极其卑狭。衰绖不去乎体。哭泣之戚。深墨之色。虽闾阎匹夫善于居丧者。亦不能过也。自古人君能行三年丧者亦少。惟晋武帝,元魏孝文及宋孝宗。以孝闻于后世。然其哀戚之至。则未必皆及于 殿下也。伏惟 殿下之至行。诚卓冠于前古。而可传于百代也。然臣民之心。虽莫不感服。而亦莫不忧恐。盖恐其 心神之伤损。气力之消减。积以日月。今虽无形见之疾病。将来之忧。岂不甚大。且凡人之气体强弱。以贵贱而不同。虽士大夫尊贵之人。与草野寒贱者迥异。况至尊之身。其居养与闾阎匹夫万万殊绝者乎。今以 至尊之居养。为闾阎匹夫之哀毁。其伤损岂不大可惧哉。且人主一身。为皇天 宗庙之所付畀。为亿兆生灵之所仰戴。必能尽于修己治人之道。使朝廷清明。民生乂安。无有一民不得其所者。跻斯世于隆古。延国祚于无疆。此人主之大孝也。然则人主一身。其重如何。诚宜慎于自保。勿致伤损。岂可比匹夫私行。徒以致于哀毁为孝乎。又况古人著居丧之节曰。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忧。盖悲哀之心。以日月杀也。自遭 大戚。今已三月矣。古人不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102H 页
 懈之期。亦将过矣。哀毁何可一向如初。伏愿 圣明深察礼经毁瘠之戒。亦念已往所伤既多。将来必有可忧。又念至尊居养与闾阎之人悬绝。又念 一身责任极重。不可同于匹夫之孝。又念日月将过不懈之期。 裁抑至情。强进食饮。七时之哭。不为尽参。务自调辅。使 圣躬强健。以期尽于大孝。如是则天地祖宗。皆为悦怿。一国臣民。无不欣欣有喜色矣。臣无任激切祈望屏营之至。
懈之期。亦将过矣。哀毁何可一向如初。伏愿 圣明深察礼经毁瘠之戒。亦念已往所伤既多。将来必有可忧。又念至尊居养与闾阎之人悬绝。又念 一身责任极重。不可同于匹夫之孝。又念日月将过不懈之期。 裁抑至情。强进食饮。七时之哭。不为尽参。务自调辅。使 圣躬强健。以期尽于大孝。如是则天地祖宗。皆为悦怿。一国臣民。无不欣欣有喜色矣。臣无任激切祈望屏营之至。请停 宗庙夏享亲祭疏
伏以凡人疾病。多生于春夏之交。以其日气寒暄之不常。衣服脱着之难适也。近来 玉候虽曰平安。前日感冒未宁之时亦殊频数。此正节适时候。加意静摄之时也。私家暂时行祭。亦有因早起感触而致伤者。况今风雨连日。日候不齐。闾阎之人。触冒生疾者甚多。于此之时。劳勤 玉体。彻夜行礼于至敬之地。其在慎保摄养之道。窃恐非宜也。今当时享之日。 躬奉明禋。以展孝思。诚出 圣上追远之至情。而日候之不能和畅如此。群下之心。皆以为虑。医官之言。亦多如此。臣之愚意。窃愿姑停 亲祭。待至秋享大祭日气舒畅之时而行之。允为合宜。不胜区区愚虑。敢
浦渚先生集卷之五 第 102L 页
 此陈达。伏愿 圣明财察焉。
此陈达。伏愿 圣明财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