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x 页
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疏(四首)
疏(四首)
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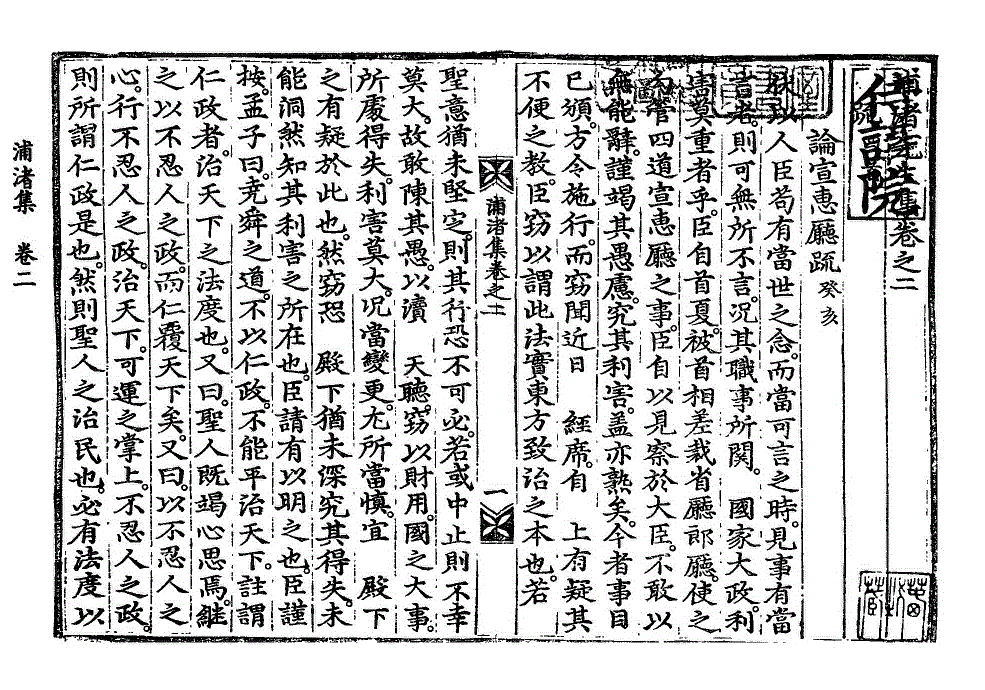 论宣惠厅疏(癸亥)
论宣惠厅疏(癸亥)伏以人臣苟有当世之念。而当可言之时。见事有当言者。则可无所不言。况其职事所关。 国家大政。利害莫重者乎。臣自首夏。被首相差裁省厅郎厅。使之句管四道宣惠厅之事。臣自以见察于大臣。不敢以无能辞。谨竭其愚虑。究其利害。盖亦熟矣。今者事目已颁。方令施行。而窃闻近日 经席。自 上有疑其不便之教。臣窃以谓此法实东方致治之本也。若 圣意犹未坚定。则其行恐不可必。若或中止则不幸莫大。故敢陈其愚。以渎 天听。窃以财用。国之大事。所处得失。利害莫大。况当变更。尤所当慎。宜 殿下之有疑于此也。然窃恐 殿下犹未深究其得失。未能洞然知其利害之所在也。臣请有以明之也。臣谨按。孟子曰。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注谓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又曰。圣人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又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不忍人之政。则所谓仁政是也。然则圣人之治民也。必有法度以
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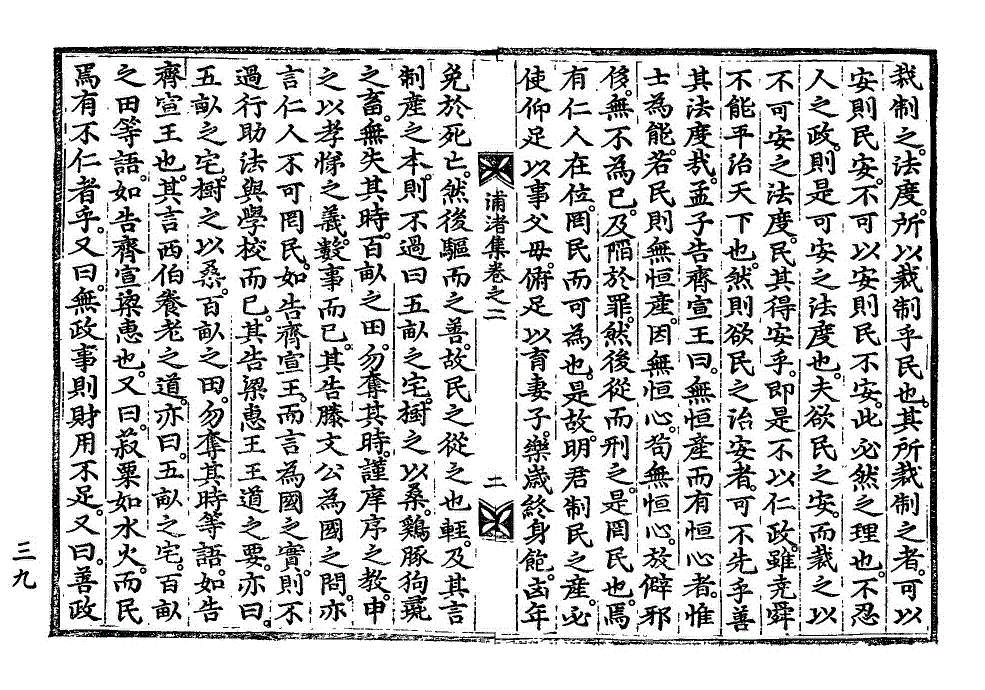 裁制之。法度。所以裁制乎民也。其所裁制之者。可以安则民安。不可以安则民不安。此必然之理也。不忍人之政。则是可安之法度也。夫欲民之安。而裁之以不可安之法度。民其得安乎。即是不以仁政。虽尧舜不能平治天下也。然则欲民之治安者。可不先乎善其法度哉。孟子告齐宣王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育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及其言制产之本。则不过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数事而已。其告滕文公为国之问。亦言仁人不可罔民。如告齐宣王。而言为国之实。则不过行助法与学校而已。其告梁惠王王道之要。亦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等语。如告齐宣王也。其言西伯养老之道。亦曰。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等语。如告齐宣,梁惠也。又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又曰。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又曰。善政
裁制之。法度。所以裁制乎民也。其所裁制之者。可以安则民安。不可以安则民不安。此必然之理也。不忍人之政。则是可安之法度也。夫欲民之安。而裁之以不可安之法度。民其得安乎。即是不以仁政。虽尧舜不能平治天下也。然则欲民之治安者。可不先乎善其法度哉。孟子告齐宣王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育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及其言制产之本。则不过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数事而已。其告滕文公为国之问。亦言仁人不可罔民。如告齐宣王。而言为国之实。则不过行助法与学校而已。其告梁惠王王道之要。亦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等语。如告齐宣王也。其言西伯养老之道。亦曰。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等语。如告齐宣,梁惠也。又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又曰。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又曰。善政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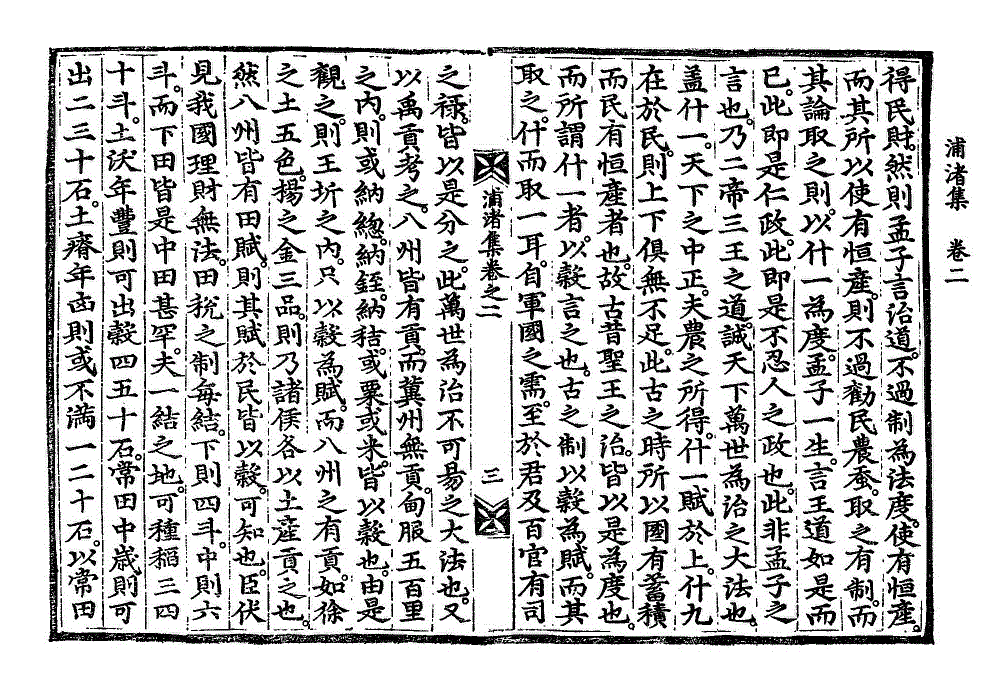 得民财。然则孟子言治道。不过制为法度。使有恒产。而其所以使有恒产。则不过劝民农蚕。取之有制。而其论取之则。以什一为度。孟子一生。言王道如是而已。此即是仁政。此即是不忍人之政也。此非孟子之言也。乃二帝三王之道。诚天下万世为治之大法也。盖什一。天下之中正。夫农之所得。什一赋于上。什九在于民。则上下俱无不足。此古之时所以国有蓄积而民有恒产者也。故古昔圣王之治。皆以是为度也。而所谓什一者。以谷言之也。古之制以谷为赋。而其取之。什而取一耳。自军国之需。至于君及百官有司之禄。皆以是分之。此万世为治不可易之大法也。又以禹贡考之。八州皆有贡。而冀州无贡。甸服五百里之内。则或纳总。纳铚。纳秸。或粟或米。皆以谷也。由是观之。则王圻之内。只以谷为赋。而八州之有贡。如徐之土五色。扬之金三品。则乃诸侯各以土产贡之也。然八州皆有田赋。则其赋于民皆以谷。可知也。臣伏见我国理财无法。田税之制每结。下则四斗。中则六斗。而下田皆是中田甚罕。夫一结之地。可种稻三四十斗。土沃年丰则可出谷四五十石。常田中岁则可出二三十石。土瘠年凶则或不满一二十石。以常田
得民财。然则孟子言治道。不过制为法度。使有恒产。而其所以使有恒产。则不过劝民农蚕。取之有制。而其论取之则。以什一为度。孟子一生。言王道如是而已。此即是仁政。此即是不忍人之政也。此非孟子之言也。乃二帝三王之道。诚天下万世为治之大法也。盖什一。天下之中正。夫农之所得。什一赋于上。什九在于民。则上下俱无不足。此古之时所以国有蓄积而民有恒产者也。故古昔圣王之治。皆以是为度也。而所谓什一者。以谷言之也。古之制以谷为赋。而其取之。什而取一耳。自军国之需。至于君及百官有司之禄。皆以是分之。此万世为治不可易之大法也。又以禹贡考之。八州皆有贡。而冀州无贡。甸服五百里之内。则或纳总。纳铚。纳秸。或粟或米。皆以谷也。由是观之。则王圻之内。只以谷为赋。而八州之有贡。如徐之土五色。扬之金三品。则乃诸侯各以土产贡之也。然八州皆有田赋。则其赋于民皆以谷。可知也。臣伏见我国理财无法。田税之制每结。下则四斗。中则六斗。而下田皆是中田甚罕。夫一结之地。可种稻三四十斗。土沃年丰则可出谷四五十石。常田中岁则可出二三十石。土瘠年凶则或不满一二十石。以常田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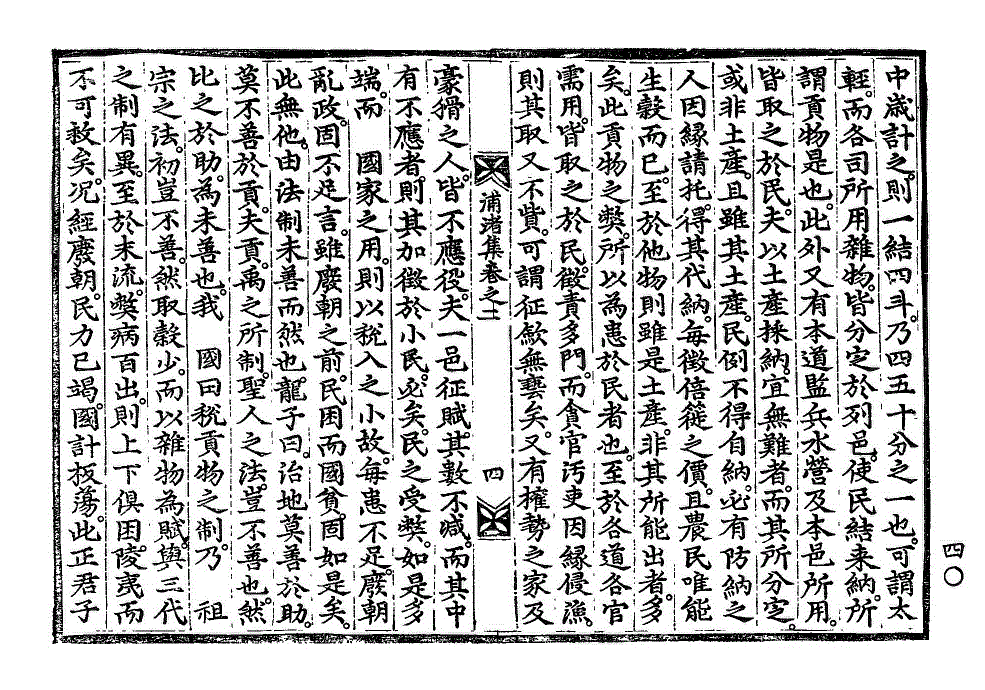 中岁计之。则一结四斗。乃四五十分之一也。可谓太轻。而各司所用杂物。皆分定于列邑。使民结来纳。所谓贡物是也。此外又有本道监兵水营及本邑所用。皆取之于民。夫以土产采纳。宜无难者。而其所分定。或非土产。且虽其土产。民例不得自纳。必有防纳之人因缘请托。得其代纳。每徵倍蓰之价。且农民唯能生谷而已。至于他物则虽是土产。非其所能出者。多矣。此贡物之弊。所以为患于民者也。至于各道各官需用。皆取之于民。徵责多门。而贪官污吏因缘侵渔。则其取又不赀。可谓征敛无艺矣。又有权势之家及豪猾之人。皆不应役。夫一邑征赋。其数不减。而其中有不应者。则其加徵于小民。必矣。民之受弊。如是多端。而 国家之用。则以税入之小故。每患不足。废朝乱政。固不足言。虽废朝之前。民困而国贫。固如是矣。此无他。由法制未善而然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夫贡。禹之所制。圣人之法。岂不善也。然比之于助。为未善也。我 国田税贡物之制。乃 祖宗之法。初岂不善。然取谷少。而以杂物为赋。与三代之制有异。至于末流。弊病百出。则上下俱困。陵夷而不可救矣。况经废朝。民力已竭。国计板荡。此正君子
中岁计之。则一结四斗。乃四五十分之一也。可谓太轻。而各司所用杂物。皆分定于列邑。使民结来纳。所谓贡物是也。此外又有本道监兵水营及本邑所用。皆取之于民。夫以土产采纳。宜无难者。而其所分定。或非土产。且虽其土产。民例不得自纳。必有防纳之人因缘请托。得其代纳。每徵倍蓰之价。且农民唯能生谷而已。至于他物则虽是土产。非其所能出者。多矣。此贡物之弊。所以为患于民者也。至于各道各官需用。皆取之于民。徵责多门。而贪官污吏因缘侵渔。则其取又不赀。可谓征敛无艺矣。又有权势之家及豪猾之人。皆不应役。夫一邑征赋。其数不减。而其中有不应者。则其加徵于小民。必矣。民之受弊。如是多端。而 国家之用。则以税入之小故。每患不足。废朝乱政。固不足言。虽废朝之前。民困而国贫。固如是矣。此无他。由法制未善而然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夫贡。禹之所制。圣人之法。岂不善也。然比之于助。为未善也。我 国田税贡物之制。乃 祖宗之法。初岂不善。然取谷少。而以杂物为赋。与三代之制有异。至于末流。弊病百出。则上下俱困。陵夷而不可救矣。况经废朝。民力已竭。国计板荡。此正君子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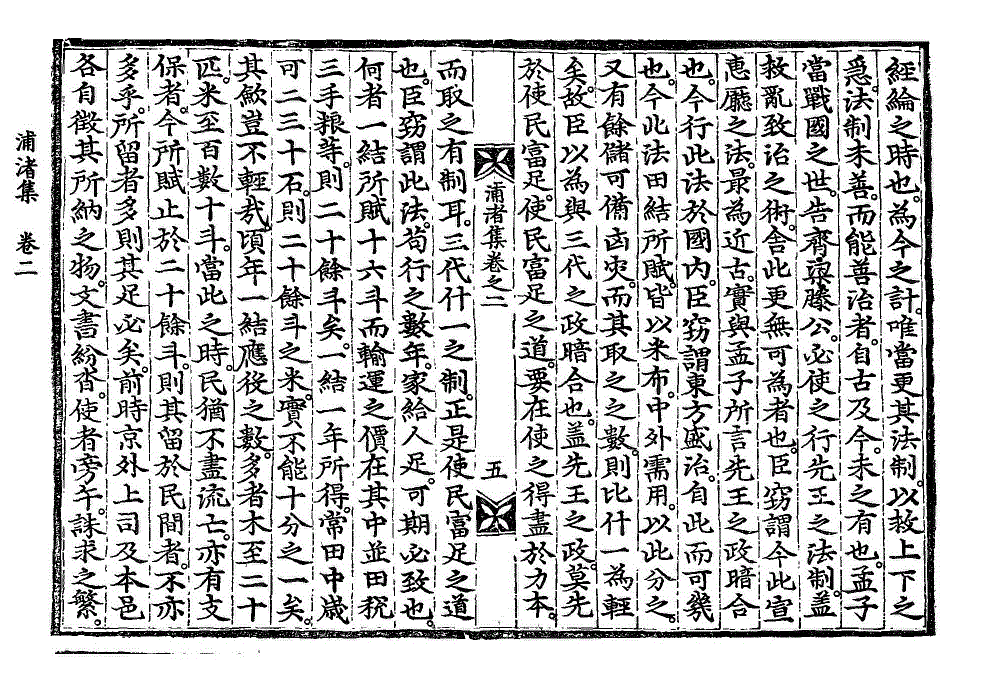 经纶之时也。为今之计。唯当更其法制。以救上下之急。法制未善。而能善治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孟子当战国之世。告齐,梁,滕公。必使之行先王之法制。盖救乱致治之术。舍此更无可为者也。臣窃谓今此宣惠厅之法。最为近古。实与孟子所言先王之政暗合也。今行此法于国内。臣窃谓东方盛治。自此而可几也。今此法田结所赋。皆以米布。中外需用。以此分之。又有馀储可备凶灾。而其取之之数。则比什一为轻矣。故臣以为与三代之政暗合也。盖先王之政。莫先于使民富足。使民富足之道。要在使之得尽于力本。而取之有制耳。三代什一之制。正是使民富足之道也。臣窃谓此法。苟行之数年。家给人足。可期必致也。何者一结所赋十六斗而输运之价在其中并田税三手粮等。则二十馀斗矣。一结一年所得。常田中岁可二三十石。则二十馀斗之米。实不能十分之一矣。其敛岂不轻哉。顷年一结应役之数。多者木至二十匹。米至百数十斗。当此之时。民犹不尽流亡。亦有支保者。今所赋止于二十馀斗。则其留于民间者。不亦多乎。所留者多则其足必矣。前时京外上司及本邑各自徵其所纳之物。文书纷沓。使者旁午。诛求之繁。
经纶之时也。为今之计。唯当更其法制。以救上下之急。法制未善。而能善治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孟子当战国之世。告齐,梁,滕公。必使之行先王之法制。盖救乱致治之术。舍此更无可为者也。臣窃谓今此宣惠厅之法。最为近古。实与孟子所言先王之政暗合也。今行此法于国内。臣窃谓东方盛治。自此而可几也。今此法田结所赋。皆以米布。中外需用。以此分之。又有馀储可备凶灾。而其取之之数。则比什一为轻矣。故臣以为与三代之政暗合也。盖先王之政。莫先于使民富足。使民富足之道。要在使之得尽于力本。而取之有制耳。三代什一之制。正是使民富足之道也。臣窃谓此法。苟行之数年。家给人足。可期必致也。何者一结所赋十六斗而输运之价在其中并田税三手粮等。则二十馀斗矣。一结一年所得。常田中岁可二三十石。则二十馀斗之米。实不能十分之一矣。其敛岂不轻哉。顷年一结应役之数。多者木至二十匹。米至百数十斗。当此之时。民犹不尽流亡。亦有支保者。今所赋止于二十馀斗。则其留于民间者。不亦多乎。所留者多则其足必矣。前时京外上司及本邑各自徵其所纳之物。文书纷沓。使者旁午。诛求之繁。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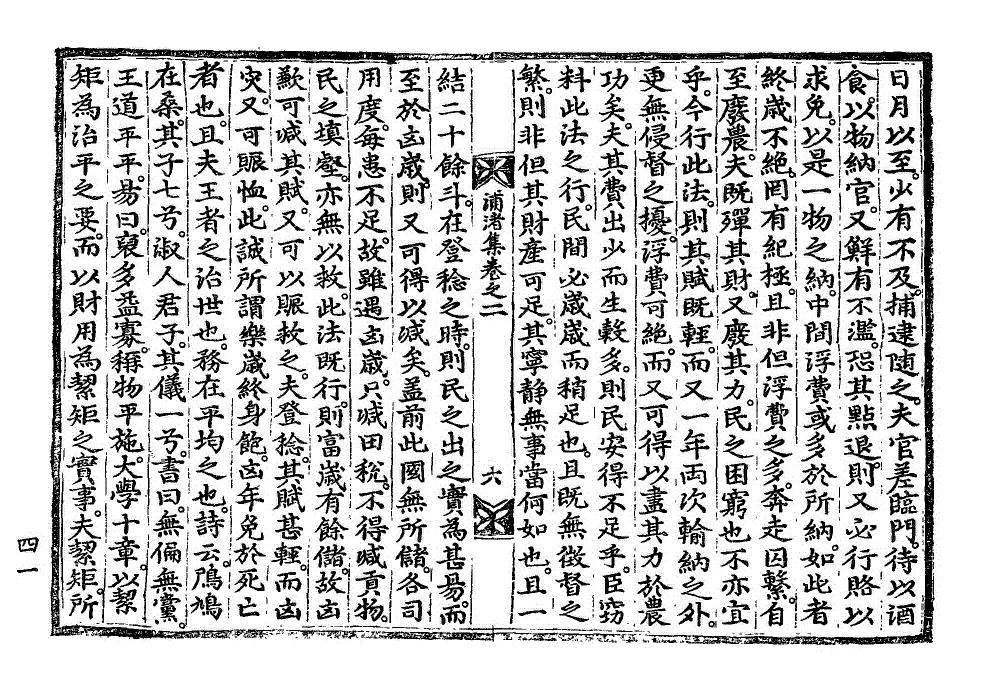 日月以至。少有不及。捕逮随之。夫官差临门。待以酒食。以物纳官。又鲜有不滥。恐其点退。则又必行赂以求免。以是一物之纳。中间浮费或多于所纳。如此者终岁不绝。罔有纪极。且非但浮费之多。奔走囚系。自至废农。夫既殚其财。又废其力。民之困穷也不亦宜乎。今行此法。则其赋既轻。而又一年两次输纳之外。更无侵督之扰。浮费可绝。而又可得以尽其力于农功矣。夫其费出少而生谷多。则民安得不足乎。臣窃料此法之行。民间必岁岁而稍足也。且既无徵督之繁。则非但其财产可足。其宁静无事当何如也。且一结二十馀斗。在登稔之时。则民之出之实为甚易。而至于凶岁。则又可得以减矣。盖前此国无所储。各司用度。每患不足。故虽遇凶岁。只田减税。不得减贡物。民之填壑。亦无以救。此法既行。则富岁有馀储。故凶歉可减其赋。又可以赈救之。夫登稔。其赋甚轻。而凶灾。又可赈恤。此诚所谓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者也。且夫王者之治世也。务在平均之也。诗云。鸤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书曰。无偏无党。王道平平。易曰。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大学十章。以絜矩为治平之要。而以财用为絜矩之实事。夫絜矩。所
日月以至。少有不及。捕逮随之。夫官差临门。待以酒食。以物纳官。又鲜有不滥。恐其点退。则又必行赂以求免。以是一物之纳。中间浮费或多于所纳。如此者终岁不绝。罔有纪极。且非但浮费之多。奔走囚系。自至废农。夫既殚其财。又废其力。民之困穷也不亦宜乎。今行此法。则其赋既轻。而又一年两次输纳之外。更无侵督之扰。浮费可绝。而又可得以尽其力于农功矣。夫其费出少而生谷多。则民安得不足乎。臣窃料此法之行。民间必岁岁而稍足也。且既无徵督之繁。则非但其财产可足。其宁静无事当何如也。且一结二十馀斗。在登稔之时。则民之出之实为甚易。而至于凶岁。则又可得以减矣。盖前此国无所储。各司用度。每患不足。故虽遇凶岁。只田减税。不得减贡物。民之填壑。亦无以救。此法既行。则富岁有馀储。故凶歉可减其赋。又可以赈救之。夫登稔。其赋甚轻。而凶灾。又可赈恤。此诚所谓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者也。且夫王者之治世也。务在平均之也。诗云。鸤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书曰。无偏无党。王道平平。易曰。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大学十章。以絜矩为治平之要。而以财用为絜矩之实事。夫絜矩。所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42H 页
 以均平之道也。孟子曰。经界不正则井地不均。谷禄不平。然则王政之所求。唯在平均。而不均。不平。实王政之所病也。盖均平则人人皆得其所。即是治也。不均不平则有幸免。有偏苦。二者皆不得所。即是乱也。焉有王政之治。有幸免而不为之制。有偏苦而不为之救哉。夫防纳之人与农民。均是民也。而防纳者。无功而坐享重利。农民。终岁勤苦而虚费倍蓰之价。此其不均不平。一也。豪势之人与小民均食王土。而豪势者不应其役。小民既应其役。而又并供豪势之役。此其不均不平。二也。以各道各邑言之。则各道出役不同。一道之中。又大邑常轻。小邑常重。其大小相似之中。亦有此重而彼轻。则此其不均不平。三也。以百官所食言之。则京官虽大臣。其禄不多。外官所食。无有限度。州郡之中。残者或不足以给妻子。富者一年所用。或至累千石。夫均是邑宰。而独使享累千石。何哉。此实无谓之甚者。此其不均不平。四也。今此法一行。则民之所赋。皆得自纳。无防纳侵欺之患。防纳者无所施其巧。则亦将自尽于农贾之业。以食其力。所谓国无游民。生之者众也。一结所赋。其制一定。豪势不得图免。小民亦免侵加。大邑小邑。无不均齐。各官
以均平之道也。孟子曰。经界不正则井地不均。谷禄不平。然则王政之所求。唯在平均。而不均。不平。实王政之所病也。盖均平则人人皆得其所。即是治也。不均不平则有幸免。有偏苦。二者皆不得所。即是乱也。焉有王政之治。有幸免而不为之制。有偏苦而不为之救哉。夫防纳之人与农民。均是民也。而防纳者。无功而坐享重利。农民。终岁勤苦而虚费倍蓰之价。此其不均不平。一也。豪势之人与小民均食王土。而豪势者不应其役。小民既应其役。而又并供豪势之役。此其不均不平。二也。以各道各邑言之。则各道出役不同。一道之中。又大邑常轻。小邑常重。其大小相似之中。亦有此重而彼轻。则此其不均不平。三也。以百官所食言之。则京官虽大臣。其禄不多。外官所食。无有限度。州郡之中。残者或不足以给妻子。富者一年所用。或至累千石。夫均是邑宰。而独使享累千石。何哉。此实无谓之甚者。此其不均不平。四也。今此法一行。则民之所赋。皆得自纳。无防纳侵欺之患。防纳者无所施其巧。则亦将自尽于农贾之业。以食其力。所谓国无游民。生之者众也。一结所赋。其制一定。豪势不得图免。小民亦免侵加。大邑小邑。无不均齐。各官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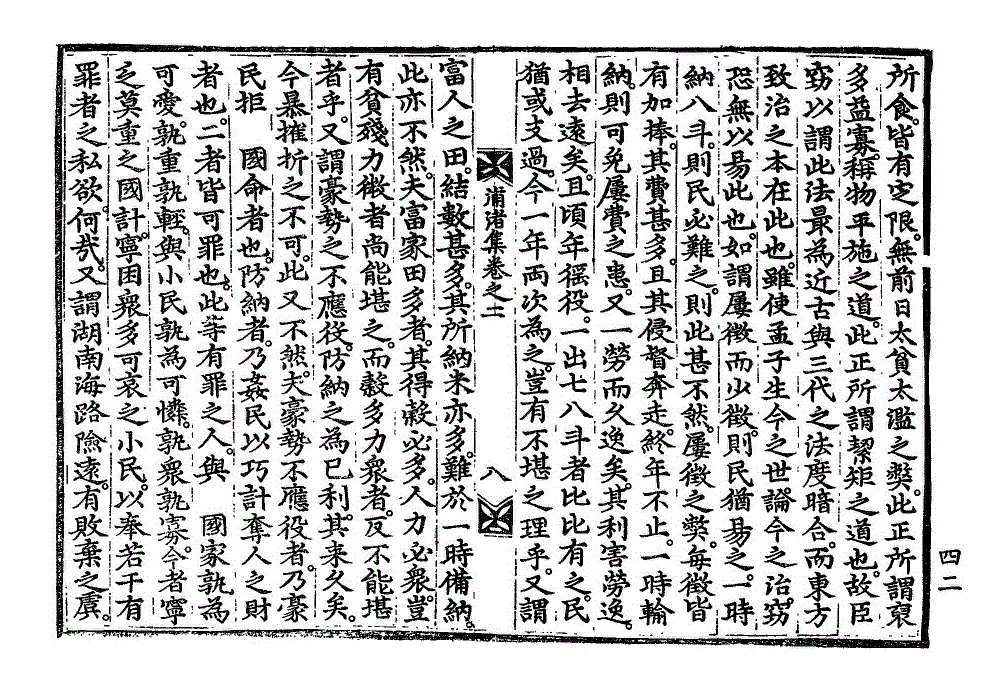 所食。皆有定限。无前日太贫太滥之弊。此正所谓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之道。此正所谓絜矩之道也。故臣窃以谓此法最为近古与三代之法度暗合。而东方致治之本在此也。虽使孟子生今之世。论今之治。窃恐无以易此也。如谓屡徵而少徵。则民犹易之。一时纳八斗。则民必难之。则此甚不然。屡徵之弊。每徵皆有加捧。其费甚多。且其侵督奔走。终年不止。一时输纳。则可免屡费之患。又一劳而久逸矣。其利害劳逸。相去远矣。且顷年徭役。一出七八斗者比比有之。民犹或支过。今一年两次为之。岂有不堪之理乎。又谓富人之田。结数甚多。其所纳米亦多。难于一时备纳。此亦不然。夫富家田多者。其得谷必多。人力必众。岂有贫残力微者尚能堪之。而谷多力众者。反不能堪者乎。又谓豪势之不应役。防纳之为己利。其来久矣。今暴摧折之不可。此又不然。夫豪势不应役者。乃豪民拒 国命者也。防纳者。乃奸民以巧计夺人之财者也。二者皆可罪也。此等有罪之人。与 国家孰为可爱。孰重孰轻。与小民孰为可怜。孰众孰寡。今者宁乏莫重之国计。宁困众多可哀之小民。以奉若干有罪者之私欲。何哉。又谓湖南海路险远。有败弃之虞。
所食。皆有定限。无前日太贫太滥之弊。此正所谓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之道。此正所谓絜矩之道也。故臣窃以谓此法最为近古与三代之法度暗合。而东方致治之本在此也。虽使孟子生今之世。论今之治。窃恐无以易此也。如谓屡徵而少徵。则民犹易之。一时纳八斗。则民必难之。则此甚不然。屡徵之弊。每徵皆有加捧。其费甚多。且其侵督奔走。终年不止。一时输纳。则可免屡费之患。又一劳而久逸矣。其利害劳逸。相去远矣。且顷年徭役。一出七八斗者比比有之。民犹或支过。今一年两次为之。岂有不堪之理乎。又谓富人之田。结数甚多。其所纳米亦多。难于一时备纳。此亦不然。夫富家田多者。其得谷必多。人力必众。岂有贫残力微者尚能堪之。而谷多力众者。反不能堪者乎。又谓豪势之不应役。防纳之为己利。其来久矣。今暴摧折之不可。此又不然。夫豪势不应役者。乃豪民拒 国命者也。防纳者。乃奸民以巧计夺人之财者也。二者皆可罪也。此等有罪之人。与 国家孰为可爱。孰重孰轻。与小民孰为可怜。孰众孰寡。今者宁乏莫重之国计。宁困众多可哀之小民。以奉若干有罪者之私欲。何哉。又谓湖南海路险远。有败弃之虞。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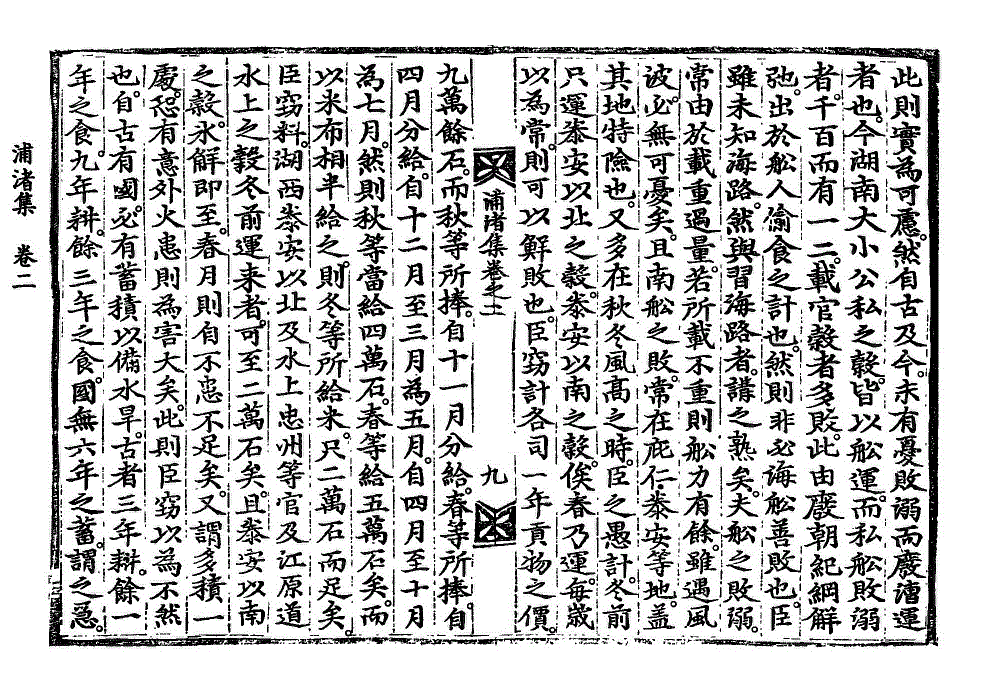 此则实为可虑。然自古及今。未有忧败溺而废漕运者也。今湖南大小公私之谷。皆以船运。而私船败溺者。千百而有一二。载官谷者多败。此由废朝纪纲解弛。出于船人偷食之计也。然则非必海船善败也。臣虽未知海路。然与习海路者。讲之熟矣。夫船之败溺。常由于载重过量。若所载不重则船力有馀。虽遇风波。必无可忧矣。且南船之败。常在庇仁,泰安等地。盖其地特险也。又多在秋冬风高之时。臣之愚计。冬前只运泰安以北之谷。泰安以南之谷。俟春乃运。每岁以为常。则可以鲜败也。臣窃计各司一年贡物之价。九万馀石。而秋等所捧。自十一月分给。春等所捧。自四月分给。自十二(一作一)月至三月为五月。自四月至十月为七月。然则秋等当给四万石。春等给五万石矣。而以米布相半给之。则冬等所给米。只二万石而足矣。臣窃料。湖西泰安以北及水上忠州等官及江原道水上之谷冬前运来者。可至二万石矣。且泰安以南之谷。冰解即至。春月则自不患不足矣。又谓多积一处。恐有意外火患则为害大矣。此则臣窃以为不然也。自古有国。必有蓄积以备水旱。古者三年耕。馀一年之食。九年耕。馀三年之食。国无六年之蓄。谓之急。
此则实为可虑。然自古及今。未有忧败溺而废漕运者也。今湖南大小公私之谷。皆以船运。而私船败溺者。千百而有一二。载官谷者多败。此由废朝纪纲解弛。出于船人偷食之计也。然则非必海船善败也。臣虽未知海路。然与习海路者。讲之熟矣。夫船之败溺。常由于载重过量。若所载不重则船力有馀。虽遇风波。必无可忧矣。且南船之败。常在庇仁,泰安等地。盖其地特险也。又多在秋冬风高之时。臣之愚计。冬前只运泰安以北之谷。泰安以南之谷。俟春乃运。每岁以为常。则可以鲜败也。臣窃计各司一年贡物之价。九万馀石。而秋等所捧。自十一月分给。春等所捧。自四月分给。自十二(一作一)月至三月为五月。自四月至十月为七月。然则秋等当给四万石。春等给五万石矣。而以米布相半给之。则冬等所给米。只二万石而足矣。臣窃料。湖西泰安以北及水上忠州等官及江原道水上之谷冬前运来者。可至二万石矣。且泰安以南之谷。冰解即至。春月则自不患不足矣。又谓多积一处。恐有意外火患则为害大矣。此则臣窃以为不然也。自古有国。必有蓄积以备水旱。古者三年耕。馀一年之食。九年耕。馀三年之食。国无六年之蓄。谓之急。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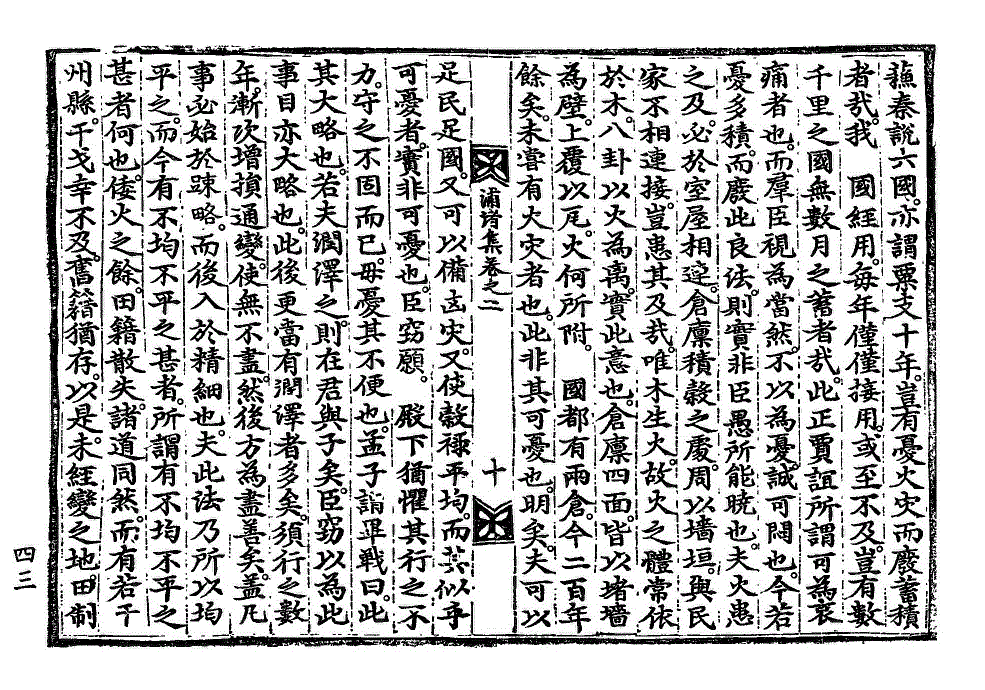 苏秦说六国。亦谓粟支十年。岂有忧火灾而废蓄积者哉。我 国经用。每年仅仅接用。或至不及。岂有数千里之国无数月之蓄者哉。此正贾谊所谓可为哀痛者也。而群臣视为当然。不以为忧。诚可闷也。今若忧多积。而废此良法。则实非臣愚所能晓也。夫火患之及。必于室屋相连。仓廪积谷之处。周以墙垣。与民家不相连接。岂患其及哉。唯木生火。故火之体常依于木。八卦以火为离。实此意也。仓廪四面。皆以堵墙为壁。上覆以瓦。火何所附。 国都有两仓。今二百年馀矣。未尝有火灾者也。此非其可忧也。明矣。夫可以足民足国。又可以备凶灾。又使谷禄平均。而其似乎可忧者。实非可忧也。臣窃愿。 殿下犹惧其行之不力。守之不固而已。毋忧其不便也。孟子谓毕战毕战曰。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臣窃以为此事目亦大略也。此后更当有润泽者多矣。须行之数年。渐次增损通变。使无不尽。然后方为尽善矣。盖凡事必始于疏略。而后入于精细也。夫此法乃所以均平之。而今有不均不平之甚者。所谓有不均不平之甚者何也。倭火之馀。田籍散失。诸道同然。而有若干州县。干戈幸不及。旧籍犹存。以是。未经变之地。田制
苏秦说六国。亦谓粟支十年。岂有忧火灾而废蓄积者哉。我 国经用。每年仅仅接用。或至不及。岂有数千里之国无数月之蓄者哉。此正贾谊所谓可为哀痛者也。而群臣视为当然。不以为忧。诚可闷也。今若忧多积。而废此良法。则实非臣愚所能晓也。夫火患之及。必于室屋相连。仓廪积谷之处。周以墙垣。与民家不相连接。岂患其及哉。唯木生火。故火之体常依于木。八卦以火为离。实此意也。仓廪四面。皆以堵墙为壁。上覆以瓦。火何所附。 国都有两仓。今二百年馀矣。未尝有火灾者也。此非其可忧也。明矣。夫可以足民足国。又可以备凶灾。又使谷禄平均。而其似乎可忧者。实非可忧也。臣窃愿。 殿下犹惧其行之不力。守之不固而已。毋忧其不便也。孟子谓毕战毕战曰。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臣窃以为此事目亦大略也。此后更当有润泽者多矣。须行之数年。渐次增损通变。使无不尽。然后方为尽善矣。盖凡事必始于疏略。而后入于精细也。夫此法乃所以均平之。而今有不均不平之甚者。所谓有不均不平之甚者何也。倭火之馀。田籍散失。诸道同然。而有若干州县。干戈幸不及。旧籍犹存。以是。未经变之地。田制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44H 页
 甚密。地少而结数多。经变之地。田制疏略。至有十石之地而不满一结者。且量田之后。垦辟者多不以籍。又吏胥招权。以起为陈者亦多。以故。民有终岁劳苦。所作尽入于徭役而犹不足者。有食焉而无赋者。有虽赋而甚轻者。此其不均不平之甚者也。须不问经变与否。通共改量。使其结卜多寡。一切均齐。而后行此法。民役始得均平。而此法乃无不尽矣。然今当草创之初。又有徵发之烦。列邑多事。民间方骚扰。不可复兴量田之役。而必待改量而后行之。则其前又无以苏民。故今且因见存田结行之。待明年而后。必须一正田制。诸道虽不可一时并量。先于一二道。期三两年尽量可也。孟子曰。仁政必自经界始。夫田制不正。民役不均。焉得为仁政。臣窃按四道田结。以戊午时起计之。四道凡三十五万馀结矣。戊午以后。流亡相继。田野荒芜。曾令诸道覈实以报。而今尚未报。未知陈田当至几结也。然赋役轻歇。民得力于农事。则臣窃料不一二年。戊午所起。可尽起矣。而隐漏疏阔之处。皆得括出。以法量之。则田结之多。当不减四五十万矣。何以知其然也。夫下三道。湖西为最小。田结几至十二万结。而岭南为最大。乃止于十馀万结。此
甚密。地少而结数多。经变之地。田制疏略。至有十石之地而不满一结者。且量田之后。垦辟者多不以籍。又吏胥招权。以起为陈者亦多。以故。民有终岁劳苦。所作尽入于徭役而犹不足者。有食焉而无赋者。有虽赋而甚轻者。此其不均不平之甚者也。须不问经变与否。通共改量。使其结卜多寡。一切均齐。而后行此法。民役始得均平。而此法乃无不尽矣。然今当草创之初。又有徵发之烦。列邑多事。民间方骚扰。不可复兴量田之役。而必待改量而后行之。则其前又无以苏民。故今且因见存田结行之。待明年而后。必须一正田制。诸道虽不可一时并量。先于一二道。期三两年尽量可也。孟子曰。仁政必自经界始。夫田制不正。民役不均。焉得为仁政。臣窃按四道田结。以戊午时起计之。四道凡三十五万馀结矣。戊午以后。流亡相继。田野荒芜。曾令诸道覈实以报。而今尚未报。未知陈田当至几结也。然赋役轻歇。民得力于农事。则臣窃料不一二年。戊午所起。可尽起矣。而隐漏疏阔之处。皆得括出。以法量之。则田结之多。当不减四五十万矣。何以知其然也。夫下三道。湖西为最小。田结几至十二万结。而岭南为最大。乃止于十馀万结。此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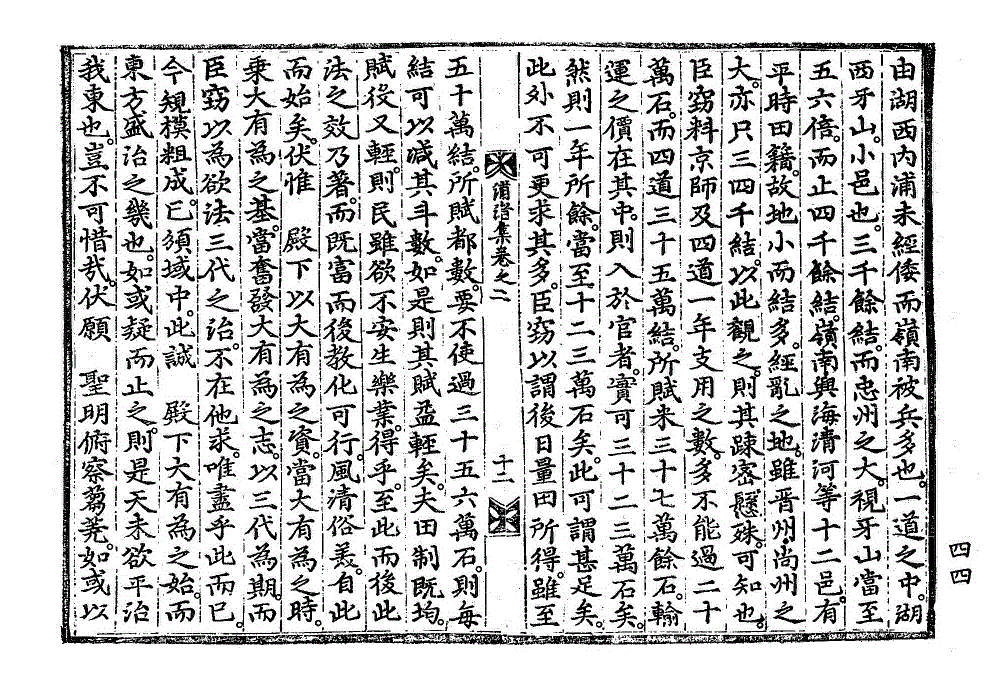 由湖西内浦未经倭而岭南被兵多也。一道之中。湖西牙山。小邑也。三千馀结。而忠州之大。视牙山当至五六倍。而止四千馀结。岭南,兴海,清河等十二邑。有平时田籍。故地小而结多。经乱之地。虽晋州,尚州之大。亦只三四千结。以此观之。则其疏密悬殊。可知也。臣窃料京师及四道一年支用之数。多不能过二十万石。而四道三十五万结。所赋米三十七万馀石。输运之价在其中。则入于官者。实可三十二三万石矣。然则一年所馀。当至十二三万石矣。此可谓甚足矣。此外不可更求其多。臣窃以谓后日量田所得。虽至五十万结。所赋都数。要不使过三十五六万石。则每结可以减其斗数。如是则其赋益轻矣。夫田制既均。赋役又轻。则民虽欲不安生乐业。得乎。至此而后此法之效乃著。而既富而后教化可行。风清俗美。自此而始矣。伏惟 殿下以大有为之资。当大有为之时。乘大有为之基。当奋发大有为之志。以三代为期。而臣窃以为欲法三代之治。不在他求。唯尽乎此而已。今规模粗成。已颁域中。此诚 殿下大有为之始。而东方盛治之几也。如或疑而止之。则是天未欲平治我东也。岂不可惜哉。伏愿 圣明俯察刍荛。如或以
由湖西内浦未经倭而岭南被兵多也。一道之中。湖西牙山。小邑也。三千馀结。而忠州之大。视牙山当至五六倍。而止四千馀结。岭南,兴海,清河等十二邑。有平时田籍。故地小而结多。经乱之地。虽晋州,尚州之大。亦只三四千结。以此观之。则其疏密悬殊。可知也。臣窃料京师及四道一年支用之数。多不能过二十万石。而四道三十五万结。所赋米三十七万馀石。输运之价在其中。则入于官者。实可三十二三万石矣。然则一年所馀。当至十二三万石矣。此可谓甚足矣。此外不可更求其多。臣窃以谓后日量田所得。虽至五十万结。所赋都数。要不使过三十五六万石。则每结可以减其斗数。如是则其赋益轻矣。夫田制既均。赋役又轻。则民虽欲不安生乐业。得乎。至此而后此法之效乃著。而既富而后教化可行。风清俗美。自此而始矣。伏惟 殿下以大有为之资。当大有为之时。乘大有为之基。当奋发大有为之志。以三代为期。而臣窃以为欲法三代之治。不在他求。唯尽乎此而已。今规模粗成。已颁域中。此诚 殿下大有为之始。而东方盛治之几也。如或疑而止之。则是天未欲平治我东也。岂不可惜哉。伏愿 圣明俯察刍荛。如或以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45H 页
 为不妄。则 圣志坚定。更勿疑挠。唯务力行。期使不忍人之泽周遍普被。则亿兆幸甚。 宗社幸甚。抑臣又闻之。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语王道。又曰。有关雎麟趾之美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盖必有是德。方有是政。苟无是德。则天理不行。人欲横流。朝不信道。工不信度。虽有美政。其安能行。然则欲行帝王之政。必修帝王之德。懋帝王之学。然后帝王之政。可得而行矣。盖古之帝王所以为圣。唯在有是德有是学有是政也。然则帝王之圣。实不难为也。懋帝王之学。修帝王之德。行帝王之政。则是亦帝王而已矣。直患人君不为之耳。臣窃见 殿下聪明之智。宽厚之仁。卓冠百王。可谓有帝王之资矣。以 殿下如是之资。懋帝王之学。致帝王之治。岂有难哉。第臣之所未知者。窃恐 圣志或有未立。不能以古之帝王自期。而或止以三代以后人主之事自处也。苟如是。则自夫心术隐微之间。至于发号施令之际。率多姑息苟且。未能一出于正。东方治化之盛。窃恐难得以望。而此法亦安保其不废也。臣窃愿圣明深究理欲善恶之分。世道治忽之几。有以明夫古昔帝王之道为可慕而为之不难。后世人主之事
为不妄。则 圣志坚定。更勿疑挠。唯务力行。期使不忍人之泽周遍普被。则亿兆幸甚。 宗社幸甚。抑臣又闻之。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语王道。又曰。有关雎麟趾之美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盖必有是德。方有是政。苟无是德。则天理不行。人欲横流。朝不信道。工不信度。虽有美政。其安能行。然则欲行帝王之政。必修帝王之德。懋帝王之学。然后帝王之政。可得而行矣。盖古之帝王所以为圣。唯在有是德有是学有是政也。然则帝王之圣。实不难为也。懋帝王之学。修帝王之德。行帝王之政。则是亦帝王而已矣。直患人君不为之耳。臣窃见 殿下聪明之智。宽厚之仁。卓冠百王。可谓有帝王之资矣。以 殿下如是之资。懋帝王之学。致帝王之治。岂有难哉。第臣之所未知者。窃恐 圣志或有未立。不能以古之帝王自期。而或止以三代以后人主之事自处也。苟如是。则自夫心术隐微之间。至于发号施令之际。率多姑息苟且。未能一出于正。东方治化之盛。窃恐难得以望。而此法亦安保其不废也。臣窃愿圣明深究理欲善恶之分。世道治忽之几。有以明夫古昔帝王之道为可慕而为之不难。后世人主之事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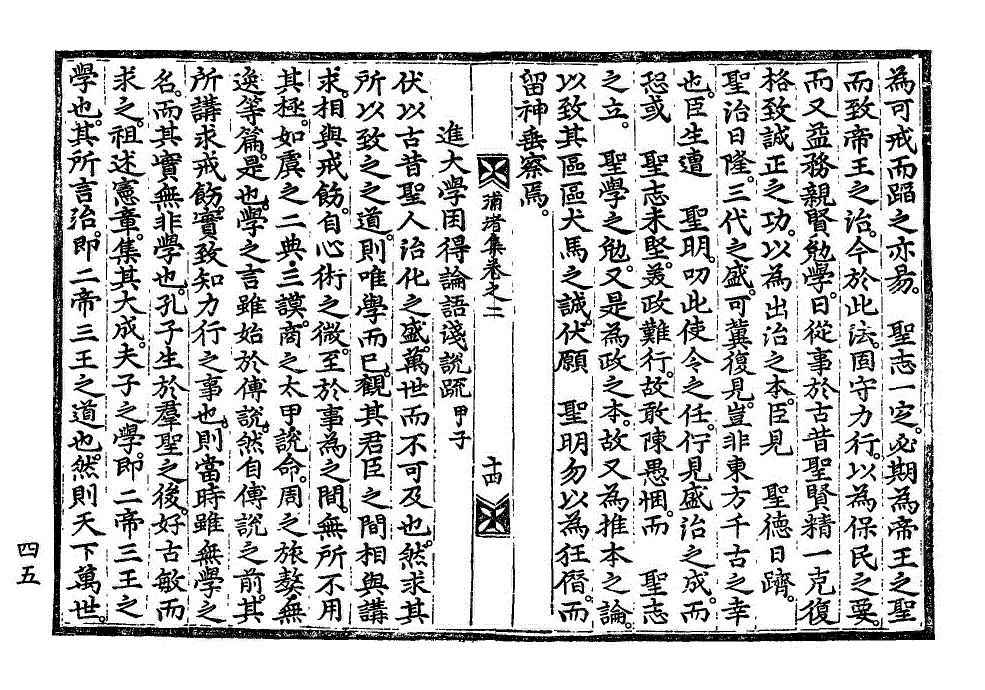 为可戒而蹈之亦易。 圣志一定。必期为帝王之圣而致帝王之治。今于此法。固守力行。以为保民之要。而又益务亲贤勉学。日从事于古昔圣贤精一克复格致诚正之功。以为出治之本。臣见 圣德日跻。 圣治日隆。三代之盛。可冀复见。岂非东方千古之幸也。臣生遭 圣明。叨此使令之任。伫见盛治之成。而恐或 圣志未坚。美政难行。故敢陈愚悃。而 圣志之立。 圣学之勉。又是为政之本。故又为推本之论。以致其区区犬马之诚。伏愿 圣明勿以为狂僭。而留神垂察焉。
为可戒而蹈之亦易。 圣志一定。必期为帝王之圣而致帝王之治。今于此法。固守力行。以为保民之要。而又益务亲贤勉学。日从事于古昔圣贤精一克复格致诚正之功。以为出治之本。臣见 圣德日跻。 圣治日隆。三代之盛。可冀复见。岂非东方千古之幸也。臣生遭 圣明。叨此使令之任。伫见盛治之成。而恐或 圣志未坚。美政难行。故敢陈愚悃。而 圣志之立。 圣学之勉。又是为政之本。故又为推本之论。以致其区区犬马之诚。伏愿 圣明勿以为狂僭。而留神垂察焉。进大学困得论语浅说疏(甲子)
伏以古昔圣人治化之盛。万世而不可及也。然求其所以致之之道。则唯学而已。观其君臣之间相与讲求。相与戒饬。自心术之微。至于事为之间。无所不用其极。如虞之二典,三谟。商之太甲,说命。周之旅獒,无逸等篇。是也。学之言虽始于傅说。然自傅说之前。其所讲求戒饬。实致知力行之事也。则当时虽无学之名。而其实无非学也。孔子生于群圣之后。好古敏而求之。祖述宪章。集其大成。夫子之学。即二帝三王之学也。其所言治。即二帝三王之道也。然则天下万世。
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46H 页
 为学为治。皆当以夫子为法而已。而论语记圣人言行。大学即圣人所说。先王所以修己治人之法者也。然则法夫子之道。不外此两书而得之。而此两书者。实天下万世为学为治之大法。伏惟 殿下志切求治。深达其要。临御以来。首讲此两书。伏见近日 殿下所以约己忧民发言制事。其不合于事理而当于人心者寡矣。虽缘 圣质纯粹。自然近道。而学问之功。亦岂可诬也。臣顷为司谏。尝一入侍 经筵。伏睹殿下于讲论经义。辨析甚精。领悟甚速。臣有以知 上圣聪明。非凡人所能及也。窃不胜感激欢悦。何幸生逢尧舜之 君。坐待隆古之治也。第臣窃有所未能知者。未知 圣志之所存。其断然以圣贤之学自任。其立心修身处事。欲一以圣贤为法欤。其或以吾之资质自美。行吾意见。自不至大违于理。不必一法古圣。而其开筵讲书。不过应故事求少补而已欤。诚能以圣贤之学自任。则其规模门路。方法次序。皆备于二书之中。虽德至于尧舜。治至于唐虞。只此二书。可以致之而有馀矣。诚能于此究其义理之蕴。以开吾之知识。察之于身心日用之间。以践其所讲之理。则其隐见表里明白纯粹。无不一出于正。如是而后
为学为治。皆当以夫子为法而已。而论语记圣人言行。大学即圣人所说。先王所以修己治人之法者也。然则法夫子之道。不外此两书而得之。而此两书者。实天下万世为学为治之大法。伏惟 殿下志切求治。深达其要。临御以来。首讲此两书。伏见近日 殿下所以约己忧民发言制事。其不合于事理而当于人心者寡矣。虽缘 圣质纯粹。自然近道。而学问之功。亦岂可诬也。臣顷为司谏。尝一入侍 经筵。伏睹殿下于讲论经义。辨析甚精。领悟甚速。臣有以知 上圣聪明。非凡人所能及也。窃不胜感激欢悦。何幸生逢尧舜之 君。坐待隆古之治也。第臣窃有所未能知者。未知 圣志之所存。其断然以圣贤之学自任。其立心修身处事。欲一以圣贤为法欤。其或以吾之资质自美。行吾意见。自不至大违于理。不必一法古圣。而其开筵讲书。不过应故事求少补而已欤。诚能以圣贤之学自任。则其规模门路。方法次序。皆备于二书之中。虽德至于尧舜。治至于唐虞。只此二书。可以致之而有馀矣。诚能于此究其义理之蕴。以开吾之知识。察之于身心日用之间。以践其所讲之理。则其隐见表里明白纯粹。无不一出于正。如是而后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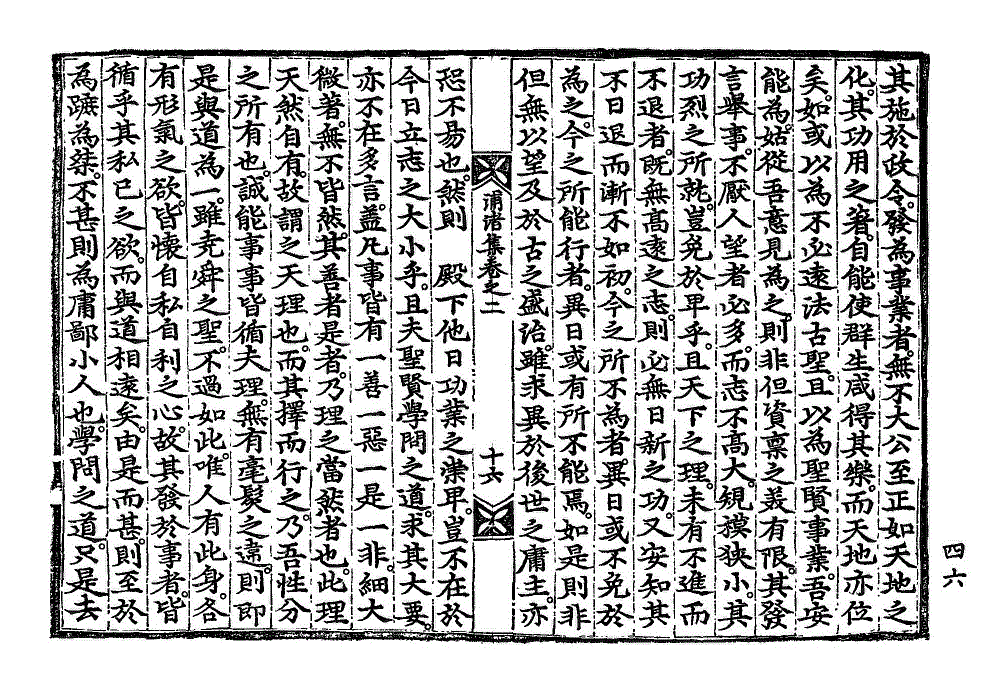 其施于政令。发为事业者。无不大公至正如天地之化。其功用之著。自能使群生咸得其乐。而天地亦位矣。如或以为不必远法古圣。且以为圣贤事业。吾安能为。姑从吾意见为之。则非但资禀之美有限。其发言举事。不厌人望者必多。而志不高大。规模狭小。其功烈之所就。岂免于卑乎。且天下之理。未有不进而不退者。既无高远之志。则必无日新之功。又安知其不日退而渐不如初。今之所不为者。异日或不免于为之。今之所能行者。异日或有所不能焉。如是则非但无以望及于古之盛治。虽求异于后世之庸主。亦恐不易也。然则 殿下他日功业之崇卑。岂不在于今日立志之大小乎。且夫圣贤学问之道。求其大要。亦不在多言。盖凡事皆有一善一恶一是一非。细大微著。无不皆然。其善者是者。乃理之当然者也。此理天然自有。故谓之天理也。而其择而行之。乃吾性分之所有也。诚能事事皆循夫理。无有毫发之违。则即是与道为一。虽尧舜之圣。不过如此。唯人有此身。各有形气之欲。皆怀自私自利之心。故其发于事者。皆循乎其私己之欲。而与道相远矣。由是而甚。则至于为蹠为桀。不甚则为庸鄙小人也。学问之道。只是去
其施于政令。发为事业者。无不大公至正如天地之化。其功用之著。自能使群生咸得其乐。而天地亦位矣。如或以为不必远法古圣。且以为圣贤事业。吾安能为。姑从吾意见为之。则非但资禀之美有限。其发言举事。不厌人望者必多。而志不高大。规模狭小。其功烈之所就。岂免于卑乎。且天下之理。未有不进而不退者。既无高远之志。则必无日新之功。又安知其不日退而渐不如初。今之所不为者。异日或不免于为之。今之所能行者。异日或有所不能焉。如是则非但无以望及于古之盛治。虽求异于后世之庸主。亦恐不易也。然则 殿下他日功业之崇卑。岂不在于今日立志之大小乎。且夫圣贤学问之道。求其大要。亦不在多言。盖凡事皆有一善一恶一是一非。细大微著。无不皆然。其善者是者。乃理之当然者也。此理天然自有。故谓之天理也。而其择而行之。乃吾性分之所有也。诚能事事皆循夫理。无有毫发之违。则即是与道为一。虽尧舜之圣。不过如此。唯人有此身。各有形气之欲。皆怀自私自利之心。故其发于事者。皆循乎其私己之欲。而与道相远矣。由是而甚。则至于为蹠为桀。不甚则为庸鄙小人也。学问之道。只是去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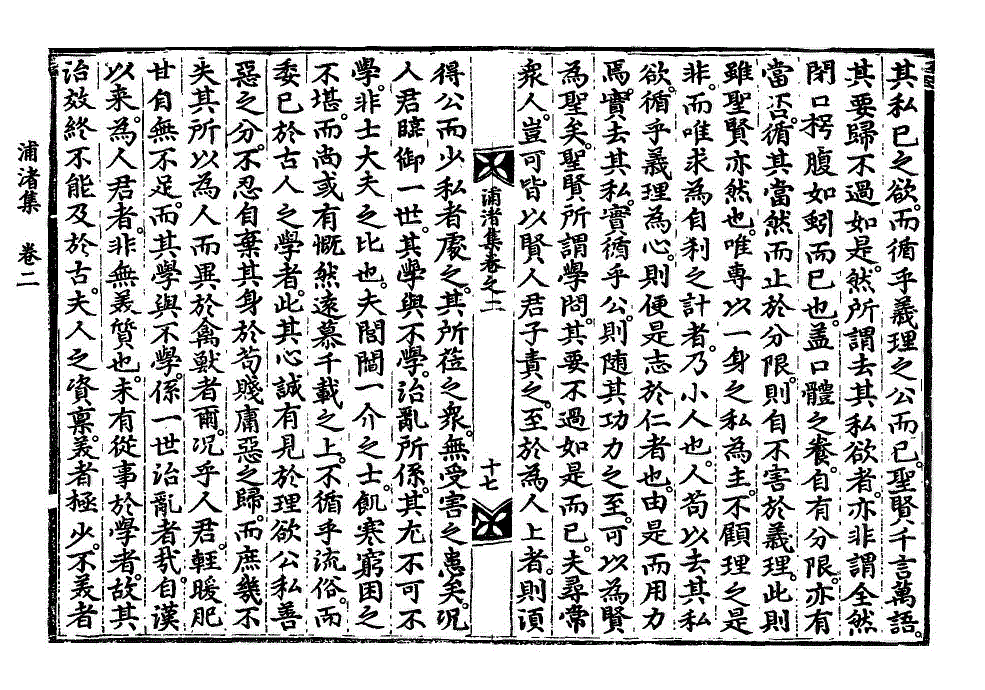 其私己之欲。而循乎义理之公而已。圣贤千言万语。其要归不过如是。然所谓去其私欲者。亦非谓全然闭口枵腹如蚓而已也。盖口体之养。自有分限。亦有当否。循其当然而止于分限。则自不害于义理。此则虽圣贤亦然也。唯专以一身之私为主。不顾理之是非。而唯求为自利之计者。乃小人也。人苟以去其私欲。循乎义理为心。则便是志于仁者也。由是而用力焉。实去其私。实循乎公。则随其功力之至。可以为贤为圣矣。圣贤所谓学问。其要不过如是而已。夫寻常众人。岂可皆以贤人君子责之。至于为人上者。则须得公而少私者处之。其所莅之众。无受害之患矣。况人君临御一世。其学与不学。治乱所系。其尤不可不学。非士大夫之比也。夫闾阎一介之士。饥寒穷困之不堪。而尚或有慨然远慕千载之上。不循乎流俗。而委己于古人之学者。此其心诚有见于理欲公私善恶之分。不忍自弃其身于苟贱庸恶之归。而庶几不失其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尔。况乎人君。轻暖肥甘自无不足。而其学与不学。系一世治乱者哉。自汉以来。为人君者。非无美质也。未有从事于学者。故其治效终不能及于古。夫人之资禀。美者极少。不美者
其私己之欲。而循乎义理之公而已。圣贤千言万语。其要归不过如是。然所谓去其私欲者。亦非谓全然闭口枵腹如蚓而已也。盖口体之养。自有分限。亦有当否。循其当然而止于分限。则自不害于义理。此则虽圣贤亦然也。唯专以一身之私为主。不顾理之是非。而唯求为自利之计者。乃小人也。人苟以去其私欲。循乎义理为心。则便是志于仁者也。由是而用力焉。实去其私。实循乎公。则随其功力之至。可以为贤为圣矣。圣贤所谓学问。其要不过如是而已。夫寻常众人。岂可皆以贤人君子责之。至于为人上者。则须得公而少私者处之。其所莅之众。无受害之患矣。况人君临御一世。其学与不学。治乱所系。其尤不可不学。非士大夫之比也。夫闾阎一介之士。饥寒穷困之不堪。而尚或有慨然远慕千载之上。不循乎流俗。而委己于古人之学者。此其心诚有见于理欲公私善恶之分。不忍自弃其身于苟贱庸恶之归。而庶几不失其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尔。况乎人君。轻暖肥甘自无不足。而其学与不学。系一世治乱者哉。自汉以来。为人君者。非无美质也。未有从事于学者。故其治效终不能及于古。夫人之资禀。美者极少。不美者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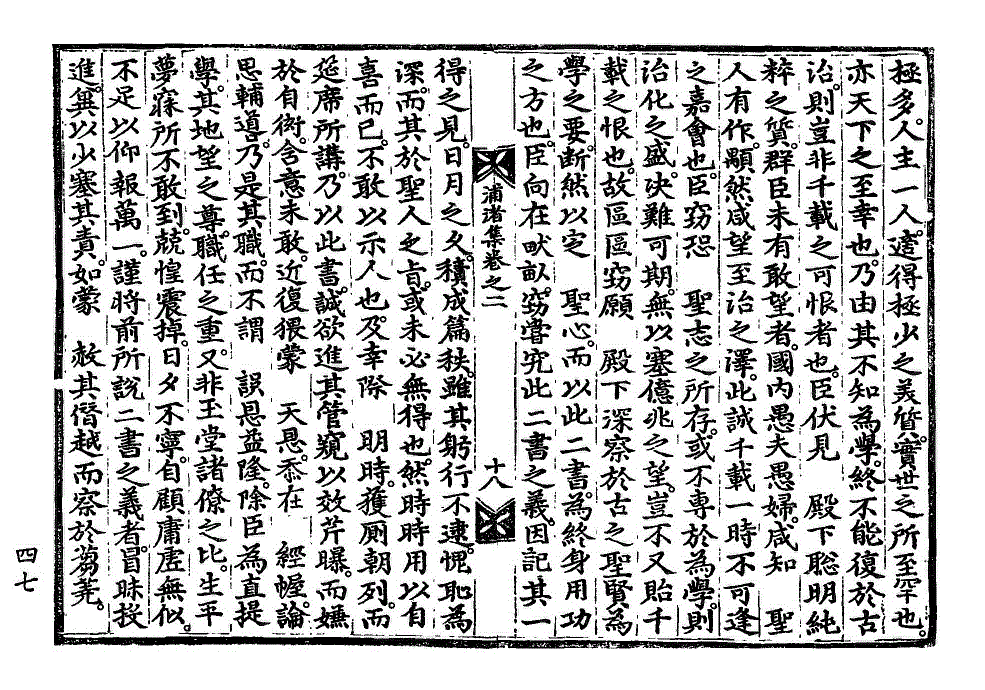 极多。人主一人。适得极少之美质。实世之所至罕也。亦天下之至幸也。乃由其不知为学。终不能复于古治。则岂非千载之可恨者也。臣伏见 殿下聪明纯粹之质。群臣未有敢望者。国内愚夫愚妇。咸知 圣人有作。颙然咸望至治之泽。此诚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也。臣窃恐 圣志之所存。或不专于为学。则治化之盛。决难可期。无以塞亿兆之望。岂不又贻千载之恨也。故区区窃愿 殿下深察于古之圣贤为学之要。断然以定 圣心。而以此二书。为终身用功之方也。臣向在畎亩。窃尝究此二书之义。因记其一得之见。日月之久。积成篇秩。虽其躬行不逮。愧耻为深。而其于圣人之旨。或未必无得也。然时时用以自喜而已。不敢以示人也。及幸际 明时。获厕朝列。而筵席所讲。乃以此书。诚欲进其管窥以效芹曝。而嫌于自衒。含意未敢。近复猥蒙 天恩。忝在 经幄。论思辅导。乃是其职。而不谓 误恩益隆。除臣为直提学。其地望之尊。职任之重。又非玉堂诸僚之比。生平梦寐所不敢到。兢惶震掉。日夕不宁。自顾庸虚无似。不足以仰报万一。谨将前所说二书之义者。冒昧投进。冀以少塞其责。如蒙 赦其僭越而察于刍荛。
极多。人主一人。适得极少之美质。实世之所至罕也。亦天下之至幸也。乃由其不知为学。终不能复于古治。则岂非千载之可恨者也。臣伏见 殿下聪明纯粹之质。群臣未有敢望者。国内愚夫愚妇。咸知 圣人有作。颙然咸望至治之泽。此诚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也。臣窃恐 圣志之所存。或不专于为学。则治化之盛。决难可期。无以塞亿兆之望。岂不又贻千载之恨也。故区区窃愿 殿下深察于古之圣贤为学之要。断然以定 圣心。而以此二书。为终身用功之方也。臣向在畎亩。窃尝究此二书之义。因记其一得之见。日月之久。积成篇秩。虽其躬行不逮。愧耻为深。而其于圣人之旨。或未必无得也。然时时用以自喜而已。不敢以示人也。及幸际 明时。获厕朝列。而筵席所讲。乃以此书。诚欲进其管窥以效芹曝。而嫌于自衒。含意未敢。近复猥蒙 天恩。忝在 经幄。论思辅导。乃是其职。而不谓 误恩益隆。除臣为直提学。其地望之尊。职任之重。又非玉堂诸僚之比。生平梦寐所不敢到。兢惶震掉。日夕不宁。自顾庸虚无似。不足以仰报万一。谨将前所说二书之义者。冒昧投进。冀以少塞其责。如蒙 赦其僭越而察于刍荛。 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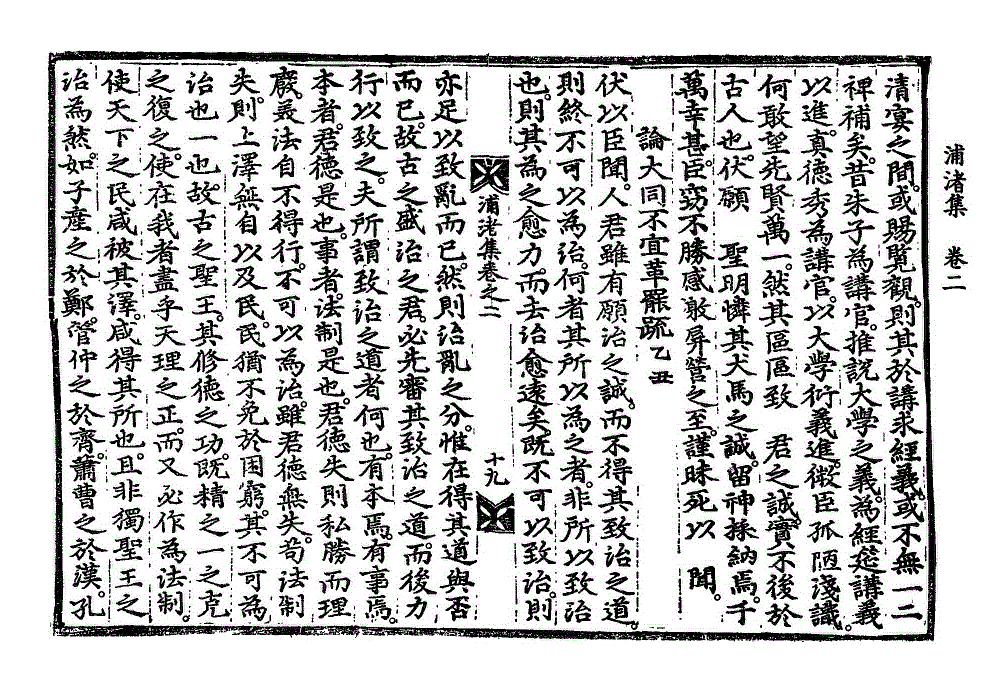 清宴之间。或赐览观。则其于讲求经义。或不无一二裨补矣。昔朱子为讲官。推说大学之义。为经筵讲义以进。真德秀为讲官。以大学衍义进。微臣孤陋浅识。何敢望先贤万一。然其区区致 君之诚。实不后于古人也。伏愿 圣明怜其犬马之诚。留神采纳焉。千万幸甚。臣窃不胜感激屏营之至。谨昧死以 闻。
清宴之间。或赐览观。则其于讲求经义。或不无一二裨补矣。昔朱子为讲官。推说大学之义。为经筵讲义以进。真德秀为讲官。以大学衍义进。微臣孤陋浅识。何敢望先贤万一。然其区区致 君之诚。实不后于古人也。伏愿 圣明怜其犬马之诚。留神采纳焉。千万幸甚。臣窃不胜感激屏营之至。谨昧死以 闻。论大同不宜革罢疏(乙丑)
伏以臣闻。人君虽有愿治之诚。而不得其致治之道。则终不可以为治。何者其所以为之者。非所以致治也。则其为之愈力。而去治愈远矣。既不可以致治。则亦足以致乱而已。然则治乱之分惟在得其道与否而已。故古之盛治之君。必先审其致治之道。而后力行以致之。夫所谓致治之道者何也。有本焉。有事焉。本者。君德是也。事者。法制是也。君德失则私胜而理废。美法自不得行。不可以为治。虽君德无失。苟法制失。则上泽无自以及民。民犹不免于困穷。其不可为治也一也。故古之圣王。其修德之功。既精之一之克之复之。使在我者尽乎天理之正。而又必作为法制。使天下之民咸被其泽。咸得其所也。且非独圣王之治为然。如子产之于郑。管仲之于齐。萧曹之于汉。孔
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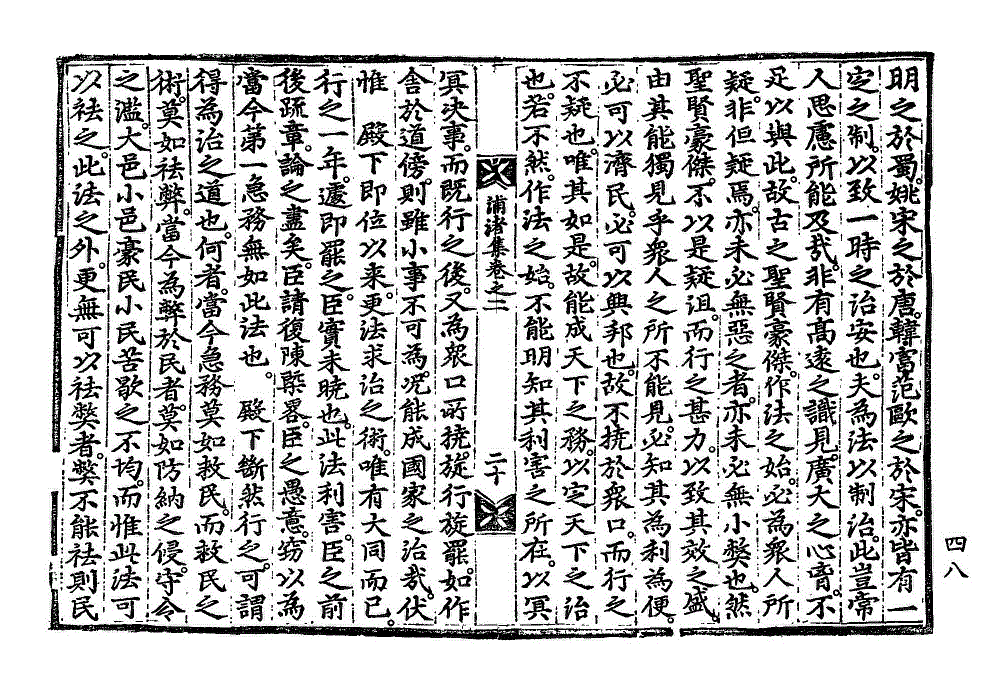 明之于蜀。姚宋之于唐。韩,富,范欧之于宋。亦皆有一定之制。以致一时之治安也。夫为法以制治。此岂常人思虑所能及哉。非有高远之识见。广大之心胸。不足以与此。故古之圣贤豪杰。作法之始。必为众人所疑。非但疑焉。亦未必无恶之者。亦未必无小弊也。然圣贤豪杰。不以是疑沮。而行之甚力。以致其效之盛。由其能独见乎众人之所不能见。必知其为利为便。必可以济民。必可以兴邦也。故不挠于众口。而行之不疑也。唯其如是。故能成天下之务。以定天下之治也。若不然。作法之始。不能明知其利害之所在。以冥冥决事。而既行之后。又为众口所挠。旋行旋罢。如作舍于道傍。则虽小事不可为。况能成国家之治哉。伏惟 殿下即位以来。更法求治之术。唯有大同而已。行之一年。遽即罢之。臣实未晓也。此法利害。臣之前后疏章。论之尽矣。臣请复陈概略。臣之愚意。窃以为当今第一急务无如此法也。 殿下断然行之。可谓得为治之道也。何者。当今急务莫如救民。而救民之术。莫如祛弊。当今为弊于民者。莫如防纳之侵。守令之滥。大邑小邑豪民小民苦歇之不均。而惟此法可以祛之。此法之外。更无可以祛弊者。弊不能祛则民
明之于蜀。姚宋之于唐。韩,富,范欧之于宋。亦皆有一定之制。以致一时之治安也。夫为法以制治。此岂常人思虑所能及哉。非有高远之识见。广大之心胸。不足以与此。故古之圣贤豪杰。作法之始。必为众人所疑。非但疑焉。亦未必无恶之者。亦未必无小弊也。然圣贤豪杰。不以是疑沮。而行之甚力。以致其效之盛。由其能独见乎众人之所不能见。必知其为利为便。必可以济民。必可以兴邦也。故不挠于众口。而行之不疑也。唯其如是。故能成天下之务。以定天下之治也。若不然。作法之始。不能明知其利害之所在。以冥冥决事。而既行之后。又为众口所挠。旋行旋罢。如作舍于道傍。则虽小事不可为。况能成国家之治哉。伏惟 殿下即位以来。更法求治之术。唯有大同而已。行之一年。遽即罢之。臣实未晓也。此法利害。臣之前后疏章。论之尽矣。臣请复陈概略。臣之愚意。窃以为当今第一急务无如此法也。 殿下断然行之。可谓得为治之道也。何者。当今急务莫如救民。而救民之术。莫如祛弊。当今为弊于民者。莫如防纳之侵。守令之滥。大邑小邑豪民小民苦歇之不均。而惟此法可以祛之。此法之外。更无可以祛弊者。弊不能祛则民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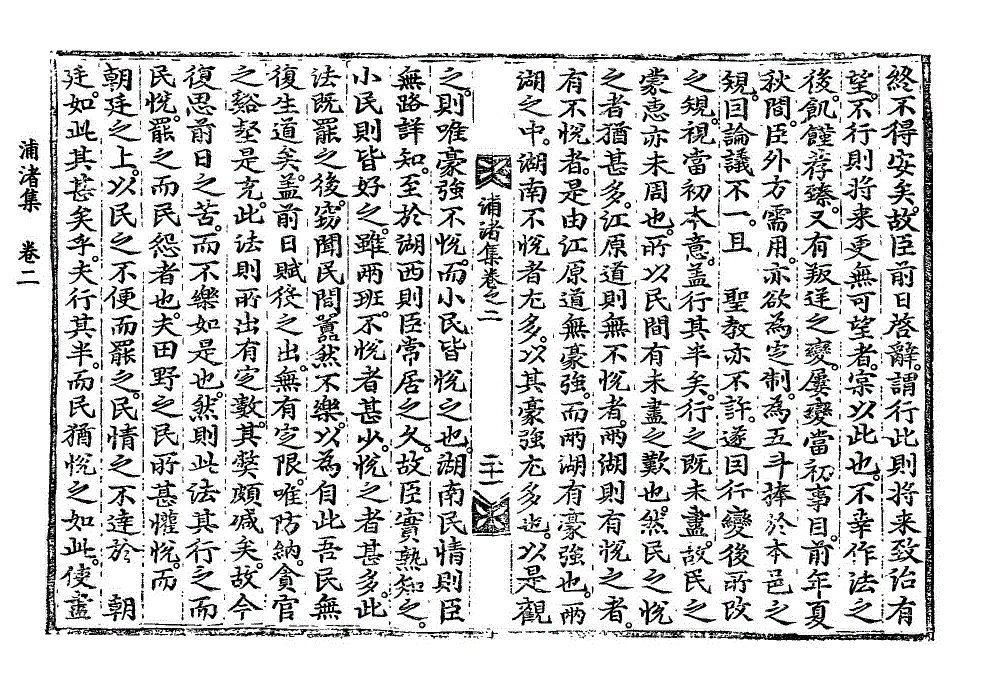 终不得安矣。故臣前日启辞。谓行此则将来致治有望。不行则将来更无可望者。实以此也。不幸作法之后。饥馑荐臻。又有叛逆之变。屡变当初事目。前年夏秋间。臣外方需用。亦欲为定制。为五斗捧于本邑之规。因论议不一。且 圣教亦不许。遂因行变后所改之规。视当初本意。盖行其半矣。行之既未尽。故民之蒙惠亦未周也。所以民间有未尽之叹也。然民之悦之者犹甚多。江原道则无不悦者。两湖则有悦之者。有不悦者。是由江原道无豪强。而两湖有豪强也。两湖之中。湖南不悦者尤多。以其豪强尤多也。以是观之。则唯豪强不悦。而小民皆悦之也。湖南民情则臣无路详知。至于湖西则臣常居之久。故臣实熟知之。小民则皆好之。虽两班。不悦者甚少。悦之者甚多。此法既罢之后。窃闻民间嚣然不乐。以为自此吾民无复生道矣。盖前日赋役之出。无有定限。唯防纳。贪官之溪壑是充。此法则所出有定数。其弊颇减矣。故今复思前日之苦。而不乐如是也。然则此法其行之而民悦。罢之而民怨者也。夫田野之民所甚欢悦。而 朝廷之上。以民之不便而罢之。民情之不达于 朝廷。如此其甚矣乎。夫行其半。而民犹悦之如此。使尽
终不得安矣。故臣前日启辞。谓行此则将来致治有望。不行则将来更无可望者。实以此也。不幸作法之后。饥馑荐臻。又有叛逆之变。屡变当初事目。前年夏秋间。臣外方需用。亦欲为定制。为五斗捧于本邑之规。因论议不一。且 圣教亦不许。遂因行变后所改之规。视当初本意。盖行其半矣。行之既未尽。故民之蒙惠亦未周也。所以民间有未尽之叹也。然民之悦之者犹甚多。江原道则无不悦者。两湖则有悦之者。有不悦者。是由江原道无豪强。而两湖有豪强也。两湖之中。湖南不悦者尤多。以其豪强尤多也。以是观之。则唯豪强不悦。而小民皆悦之也。湖南民情则臣无路详知。至于湖西则臣常居之久。故臣实熟知之。小民则皆好之。虽两班。不悦者甚少。悦之者甚多。此法既罢之后。窃闻民间嚣然不乐。以为自此吾民无复生道矣。盖前日赋役之出。无有定限。唯防纳。贪官之溪壑是充。此法则所出有定数。其弊颇减矣。故今复思前日之苦。而不乐如是也。然则此法其行之而民悦。罢之而民怨者也。夫田野之民所甚欢悦。而 朝廷之上。以民之不便而罢之。民情之不达于 朝廷。如此其甚矣乎。夫行其半。而民犹悦之如此。使尽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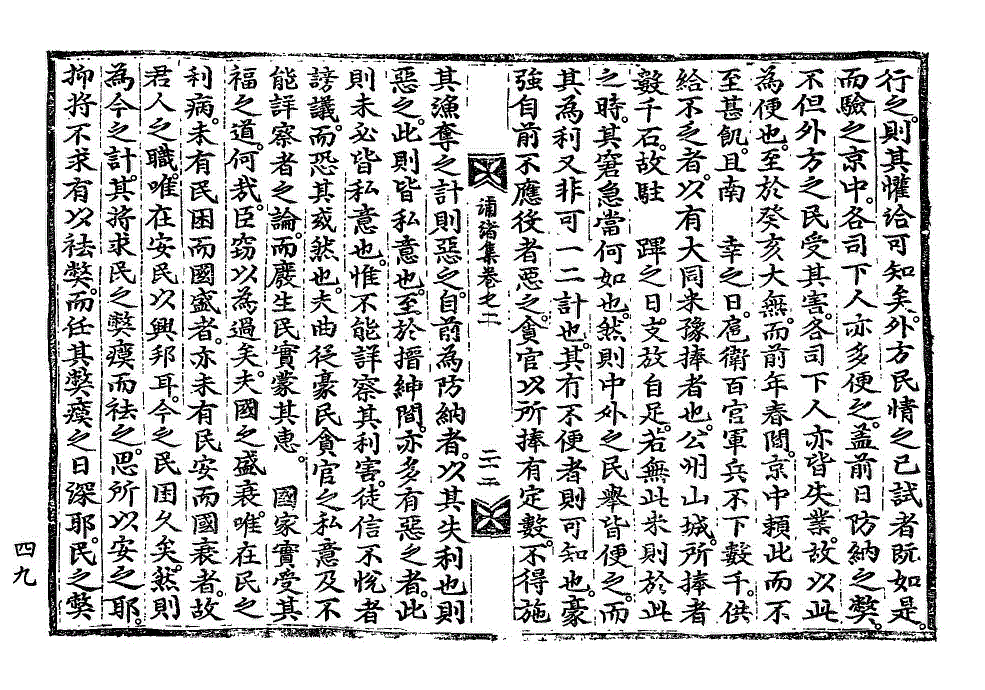 行之。则其欢洽可知矣。外方民情之已试者既如是。而验之京中。各司下人亦多便之。盖前日防纳之弊。不但外方之民受其害。各司下人亦皆失业。故以此为便也。至于癸亥大无。而前年春间。京中赖此而不至甚饥。且南 幸之日。扈卫百官军兵不下数千。供给不乏者。以有大同米豫捧者也。公州山城。所捧者数千石。故驻 跸之日。支放自足。若无此米则于此之时。其窘急当何如也。然则中外之民举皆便之。而其为利又非可一二计也。其有不便者则可知也。豪强自前不应役者恶之。贪官以所捧有定数。不得施其渔夺之计则恶之。自前为防纳者。以其失利也则恶之。此则皆私意也。至于搢绅间。亦多有恶之者。此则未必皆私意也。惟不能详察其利害。徒信不悦者谤议。而恐其或然也。夫曲从豪民贪官之私意及不能详察者之论。而废生民实蒙其惠。 国家实受其福之道。何哉。臣窃以为过矣。夫国之盛衰。唯在民之利病。未有民困而国盛者。亦未有民安而国衰者。故君人之职。唯在安民以兴邦耳。今之民困久矣。然则为今之计。其将求民之弊瘼而祛之。思所以安之耶。抑将不求有以祛弊。而任其弊瘼之日深耶。民之弊
行之。则其欢洽可知矣。外方民情之已试者既如是。而验之京中。各司下人亦多便之。盖前日防纳之弊。不但外方之民受其害。各司下人亦皆失业。故以此为便也。至于癸亥大无。而前年春间。京中赖此而不至甚饥。且南 幸之日。扈卫百官军兵不下数千。供给不乏者。以有大同米豫捧者也。公州山城。所捧者数千石。故驻 跸之日。支放自足。若无此米则于此之时。其窘急当何如也。然则中外之民举皆便之。而其为利又非可一二计也。其有不便者则可知也。豪强自前不应役者恶之。贪官以所捧有定数。不得施其渔夺之计则恶之。自前为防纳者。以其失利也则恶之。此则皆私意也。至于搢绅间。亦多有恶之者。此则未必皆私意也。惟不能详察其利害。徒信不悦者谤议。而恐其或然也。夫曲从豪民贪官之私意及不能详察者之论。而废生民实蒙其惠。 国家实受其福之道。何哉。臣窃以为过矣。夫国之盛衰。唯在民之利病。未有民困而国盛者。亦未有民安而国衰者。故君人之职。唯在安民以兴邦耳。今之民困久矣。然则为今之计。其将求民之弊瘼而祛之。思所以安之耶。抑将不求有以祛弊。而任其弊瘼之日深耶。民之弊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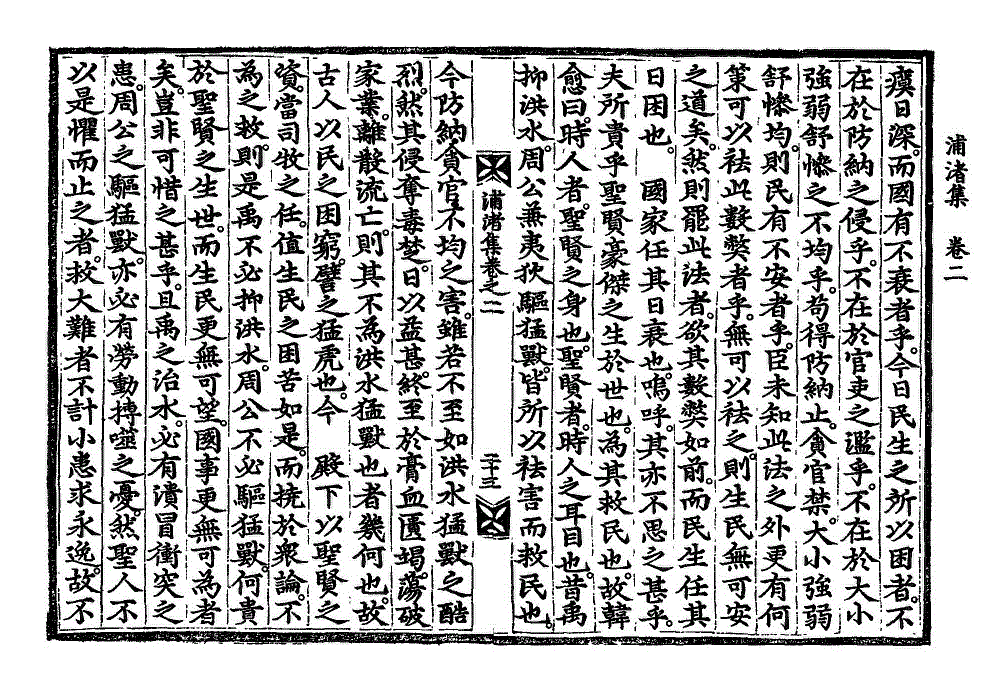 瘼日深。而国有不衰者乎。今日民生之所以困者。不在于防纳之侵乎。不在于官吏之滥乎。不在于大小强弱舒惨之不均乎。苟得防纳止。贪官禁。大小强弱舒惨均。则民有不安者乎。臣未知此法之外更有何策可以祛此数弊者乎。无可以祛之。则生民无可安之道矣。然则罢此法者。欲其数弊如前。而民生任其日困也。 国家任其日衰也。呜呼。其亦不思之甚乎。夫所贵乎圣贤豪杰之生于世也。为其救民也。故韩愈曰。时人者。圣贤之身也。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皆所以祛害而救民也。今防纳,贪官,不均之害。虽若不至如洪水猛兽之酷烈。然其侵夺毒楚。日以益甚。终至于膏血匮竭。荡破家业。离散流亡。则其不为洪水猛兽也者几何也。故古人以民之困穷。譬之猛虎地。今 殿下以圣贤之资。当司牧之任。值生民之困苦如是。而挠于众论。不为之救。则是禹不必抑洪水。周公不必驱猛兽。何贵于圣贤之生世。而生民更无可望。国事更无可为者矣。岂非可惜之甚乎。且禹之治水。必有溃冒冲突之患。周公之驱猛兽。亦必有劳动搏噬之忧。然圣人不以是惧而止之者。救大难者不计小患求永逸。故不
瘼日深。而国有不衰者乎。今日民生之所以困者。不在于防纳之侵乎。不在于官吏之滥乎。不在于大小强弱舒惨之不均乎。苟得防纳止。贪官禁。大小强弱舒惨均。则民有不安者乎。臣未知此法之外更有何策可以祛此数弊者乎。无可以祛之。则生民无可安之道矣。然则罢此法者。欲其数弊如前。而民生任其日困也。 国家任其日衰也。呜呼。其亦不思之甚乎。夫所贵乎圣贤豪杰之生于世也。为其救民也。故韩愈曰。时人者。圣贤之身也。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皆所以祛害而救民也。今防纳,贪官,不均之害。虽若不至如洪水猛兽之酷烈。然其侵夺毒楚。日以益甚。终至于膏血匮竭。荡破家业。离散流亡。则其不为洪水猛兽也者几何也。故古人以民之困穷。譬之猛虎地。今 殿下以圣贤之资。当司牧之任。值生民之困苦如是。而挠于众论。不为之救。则是禹不必抑洪水。周公不必驱猛兽。何贵于圣贤之生世。而生民更无可望。国事更无可为者矣。岂非可惜之甚乎。且禹之治水。必有溃冒冲突之患。周公之驱猛兽。亦必有劳动搏噬之忧。然圣人不以是惧而止之者。救大难者不计小患求永逸。故不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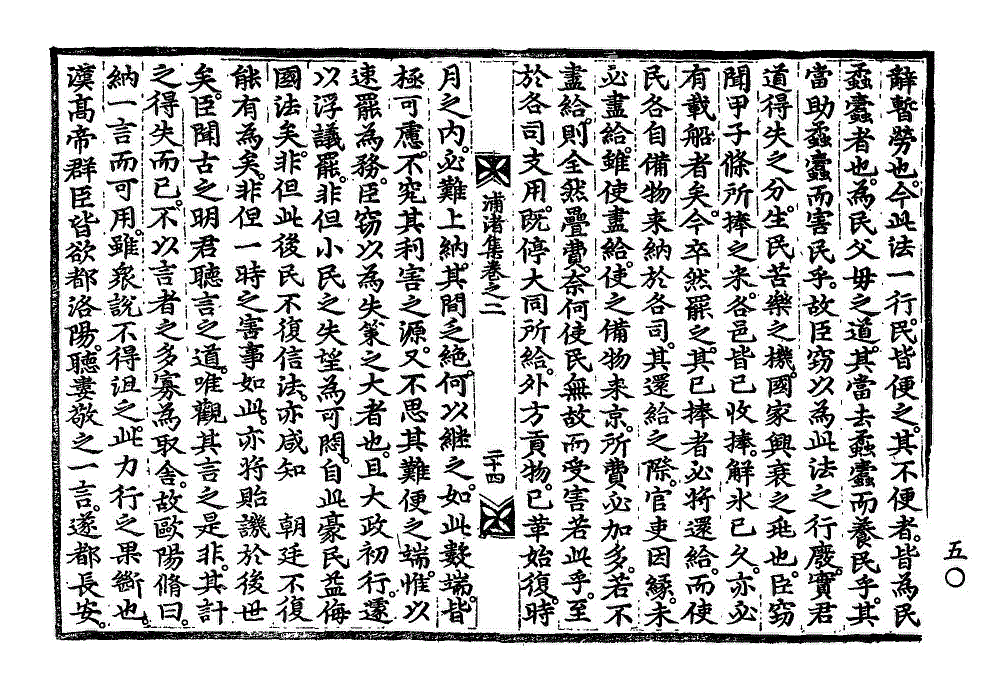 辞暂劳也。今此法一行。民皆便之。其不便者。皆为民蟊蠹者也。为民父母之道。其当去蟊蠹而养民乎。其当助蟊蠹而害民乎。故臣窃以为此法之行废。实君道得失之分。生民苦乐之机。国家兴衰之兆也。臣窃闻甲子条所捧之米。各邑皆已收捧。解冰已久。亦必有载船者矣。今卒然罢之。其已捧者必将还给。而使民各自备物来纳于各司。其还给之际。官吏因缘。未必尽给。虽使尽给。使之备物来京。所费必加多。若不尽给。则全然叠费。奈何使民无故而受害若此乎。至于各司支用。既停大同所给。外方贡物。已革始复。时月之内。必难上纳。其间乏绝。何以继之。如此数端。皆极可虑。不究其利害之源。又不思其难便之端。惟以速罢为务。臣窃以为失策之大者也。且大政初行。遽以浮议罢。非但小民之失望为可闷。自此豪民益侮国法矣。非但此后民不复信法。亦咸知 朝廷不复能有为矣。非但一时之害事如此。亦将贻讥于后世矣。臣闻古之明君听言之道。唯观其言之是非。其计之得失而已。不以言者之多寡为取舍。故欧阳脩曰。纳一言而可用。虽众说不得沮之。此力行之果断也。汉高帝群臣皆欲都洛阳。听娄敬之一言。遂都长安。
辞暂劳也。今此法一行。民皆便之。其不便者。皆为民蟊蠹者也。为民父母之道。其当去蟊蠹而养民乎。其当助蟊蠹而害民乎。故臣窃以为此法之行废。实君道得失之分。生民苦乐之机。国家兴衰之兆也。臣窃闻甲子条所捧之米。各邑皆已收捧。解冰已久。亦必有载船者矣。今卒然罢之。其已捧者必将还给。而使民各自备物来纳于各司。其还给之际。官吏因缘。未必尽给。虽使尽给。使之备物来京。所费必加多。若不尽给。则全然叠费。奈何使民无故而受害若此乎。至于各司支用。既停大同所给。外方贡物。已革始复。时月之内。必难上纳。其间乏绝。何以继之。如此数端。皆极可虑。不究其利害之源。又不思其难便之端。惟以速罢为务。臣窃以为失策之大者也。且大政初行。遽以浮议罢。非但小民之失望为可闷。自此豪民益侮国法矣。非但此后民不复信法。亦咸知 朝廷不复能有为矣。非但一时之害事如此。亦将贻讥于后世矣。臣闻古之明君听言之道。唯观其言之是非。其计之得失而已。不以言者之多寡为取舍。故欧阳脩曰。纳一言而可用。虽众说不得沮之。此力行之果断也。汉高帝群臣皆欲都洛阳。听娄敬之一言。遂都长安。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51H 页
 唐宪宗淮西之叛。廷臣皆请因而授之。听裴度,韩愈之说。遂讨平之。今此法之可行。则非独臣之言也。廷臣之以为可者。亦非一二人也。且此法初出于领议政臣李元翼之议。而行之京圻今且二十年。而民愈悦之。恐其或罢。今试三道。民情亦举便之。其为可行。窃恐无疑。此国之大事。兴衰治乱。所系极重。其行其罢。皆当极其审慎。岂可不深察其利害便否之实。而徒信人言。以决取舍。窃愿 殿下熟察臣之所言及请罢之说。其是非得失如何。行之利害如何。罢之利害如何。如见行之必有害。罢之必有益。则罢之可也。如见行之致治有望。罢之更无以救民。 国家日就衰替。如臣之所陈。则岂可罢之。使国势衰替而不振乎。罢之之议出于 庙堂。而臣敢言其非计者。臣窃谓 庙堂之意。亦非出于私也。特以动于浮议。而未及精究其利害之实。恐其或不便耳。如果觉其利害如是。则未必不以臣言为是也。且此国之大事。苟有所见。皆当言之以利于国。岂可以异于 庙堂为嫌而不言乎。此法之行废。于臣一身。非有损益。且众论不一。谤议汹汹。人莫敢坚持其说。而独臣终始以为可行。不避人之笑侮怨怒者。此岂有他哉。特其区区
唐宪宗淮西之叛。廷臣皆请因而授之。听裴度,韩愈之说。遂讨平之。今此法之可行。则非独臣之言也。廷臣之以为可者。亦非一二人也。且此法初出于领议政臣李元翼之议。而行之京圻今且二十年。而民愈悦之。恐其或罢。今试三道。民情亦举便之。其为可行。窃恐无疑。此国之大事。兴衰治乱。所系极重。其行其罢。皆当极其审慎。岂可不深察其利害便否之实。而徒信人言。以决取舍。窃愿 殿下熟察臣之所言及请罢之说。其是非得失如何。行之利害如何。罢之利害如何。如见行之必有害。罢之必有益。则罢之可也。如见行之致治有望。罢之更无以救民。 国家日就衰替。如臣之所陈。则岂可罢之。使国势衰替而不振乎。罢之之议出于 庙堂。而臣敢言其非计者。臣窃谓 庙堂之意。亦非出于私也。特以动于浮议。而未及精究其利害之实。恐其或不便耳。如果觉其利害如是。则未必不以臣言为是也。且此国之大事。苟有所见。皆当言之以利于国。岂可以异于 庙堂为嫌而不言乎。此法之行废。于臣一身。非有损益。且众论不一。谤议汹汹。人莫敢坚持其说。而独臣终始以为可行。不避人之笑侮怨怒者。此岂有他哉。特其区区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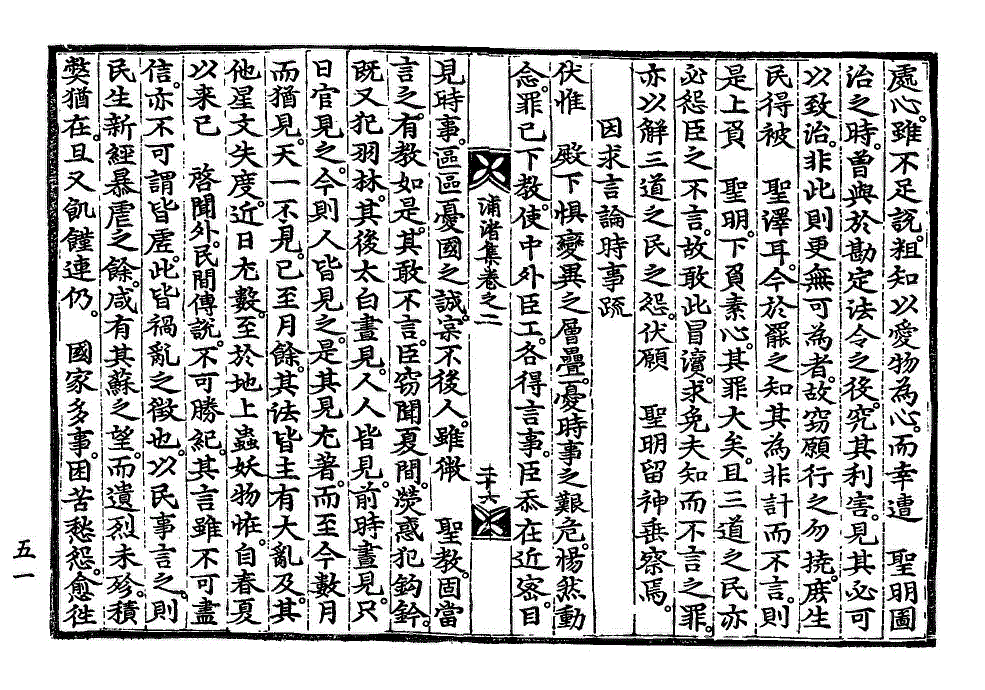 处心。虽不足说。粗知以爱物为心。而幸遭 圣明图治之时。曾与于勘定法令之役。究其利害。见其必可以致治。非此则更无可为者。故窃愿行之勿挠。庶生民得被 圣泽耳。今于罢之知其为非计而不言。则是上负 圣明。下负素心。其罪大矣。且三道之民亦必怨臣之不言。故敢此冒渎。求免夫知而不言之罪。亦以解三道之民之怨。伏愿 圣明留神垂察焉。
处心。虽不足说。粗知以爱物为心。而幸遭 圣明图治之时。曾与于勘定法令之役。究其利害。见其必可以致治。非此则更无可为者。故窃愿行之勿挠。庶生民得被 圣泽耳。今于罢之知其为非计而不言。则是上负 圣明。下负素心。其罪大矣。且三道之民亦必怨臣之不言。故敢此冒渎。求免夫知而不言之罪。亦以解三道之民之怨。伏愿 圣明留神垂察焉。因求言论时事疏
伏惟 殿下惧变异之层叠。忧时事之艰危。惕然动念。罪己下教。使中外臣工。各得言事。臣忝在近密。目见时事。区区忧国之诚。实不后人。虽微 圣教。固当言之。有教如是。其敢不言。臣窃闻夏间。荧惑犯钩钤。既又犯羽林。其后太白昼见。人人皆见。前时昼见。只日官见之。今则人皆见之。是其见尤著。而至今数月而犹见。天一不见。已至月馀。其法皆主有大乱及。其他星文失度。近日尤数。至于地上虫妖物怪。自春夏以来已 启闻外。民间传说。不可胜纪。其言虽不可尽信。亦不可谓皆虚。此皆祸乱之徵也。以民事言之。则民生新经暴虐之馀。咸有其苏之望。而遗烈未殄。积弊犹在。且又饥馑连仍。 国家多事。困苦愁怨。愈往
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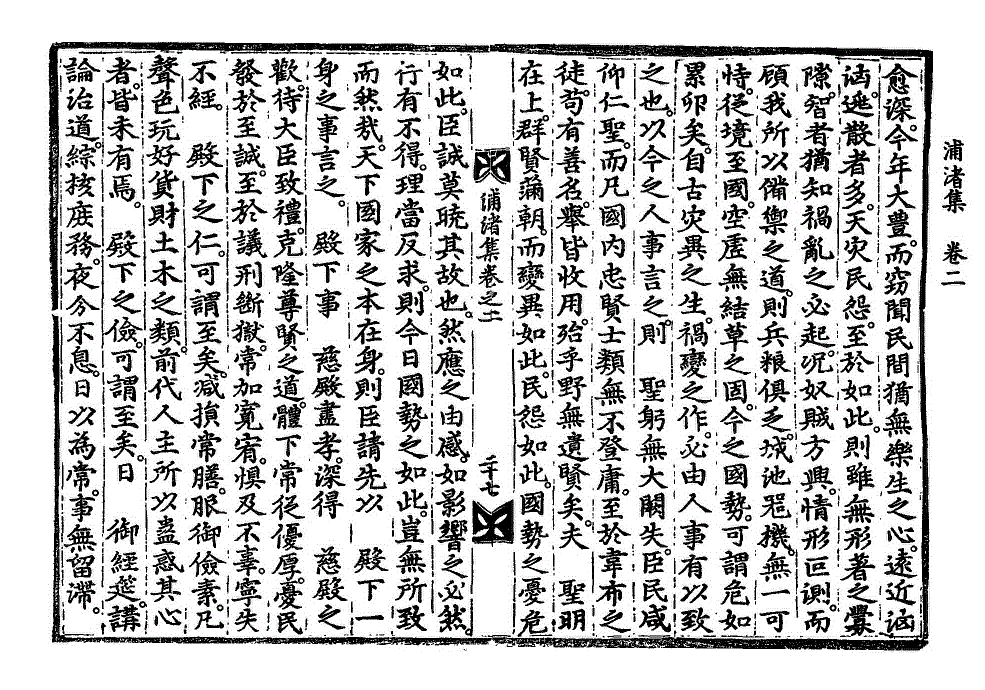 愈深。今年大丰。而窃闻民间犹无乐生之心。远近汹汹。逃散者多。天灾民怨。至于如此。则虽无形著之衅隙。智者犹知祸乱之必起。况奴贼方兴。情形叵测。而顾我所以备御之道。则兵粮俱乏。城池器机。无一可恃。从境至国。空虚无结草之固。今之国势。可谓危如累卵矣。自古灾异之生。祸变之作。必由人事有以致之也。以今之人事言之。则 圣躬无大阙失。臣民咸仰仁圣。而凡国内忠贤士类无不登庸。至于韦布之徒。苟有善名。举皆收用。殆乎野无遗贤矣。夫 圣明在上。群贤满朝。而变异如此。民怨如此。国势之忧危如此。臣诚莫晓其故也。然应之由感。如影响之必然。行有不得。理当反求。则今日国势之如此。岂无所致而然哉。天下国家之本在身。则臣请先以 殿下一身之事言之。 殿下事 慈殿尽孝。深得 慈殿之欢。待大臣致礼。克隆尊贤之道。体下常从优厚。忧民发于至诚。至于议刑断狱。常加宽宥。惧及不辜。宁失不经。 殿下之仁。可谓至矣。减损常膳。服御俭素。凡声色玩好货财土木之类。前代人主所以蛊惑其心者。皆未有焉。 殿下之俭。可谓至矣。日 御经筵。讲论治道。综核庶务。夜分不息。日以为常。事无留滞。
愈深。今年大丰。而窃闻民间犹无乐生之心。远近汹汹。逃散者多。天灾民怨。至于如此。则虽无形著之衅隙。智者犹知祸乱之必起。况奴贼方兴。情形叵测。而顾我所以备御之道。则兵粮俱乏。城池器机。无一可恃。从境至国。空虚无结草之固。今之国势。可谓危如累卵矣。自古灾异之生。祸变之作。必由人事有以致之也。以今之人事言之。则 圣躬无大阙失。臣民咸仰仁圣。而凡国内忠贤士类无不登庸。至于韦布之徒。苟有善名。举皆收用。殆乎野无遗贤矣。夫 圣明在上。群贤满朝。而变异如此。民怨如此。国势之忧危如此。臣诚莫晓其故也。然应之由感。如影响之必然。行有不得。理当反求。则今日国势之如此。岂无所致而然哉。天下国家之本在身。则臣请先以 殿下一身之事言之。 殿下事 慈殿尽孝。深得 慈殿之欢。待大臣致礼。克隆尊贤之道。体下常从优厚。忧民发于至诚。至于议刑断狱。常加宽宥。惧及不辜。宁失不经。 殿下之仁。可谓至矣。减损常膳。服御俭素。凡声色玩好货财土木之类。前代人主所以蛊惑其心者。皆未有焉。 殿下之俭。可谓至矣。日 御经筵。讲论治道。综核庶务。夜分不息。日以为常。事无留滞。 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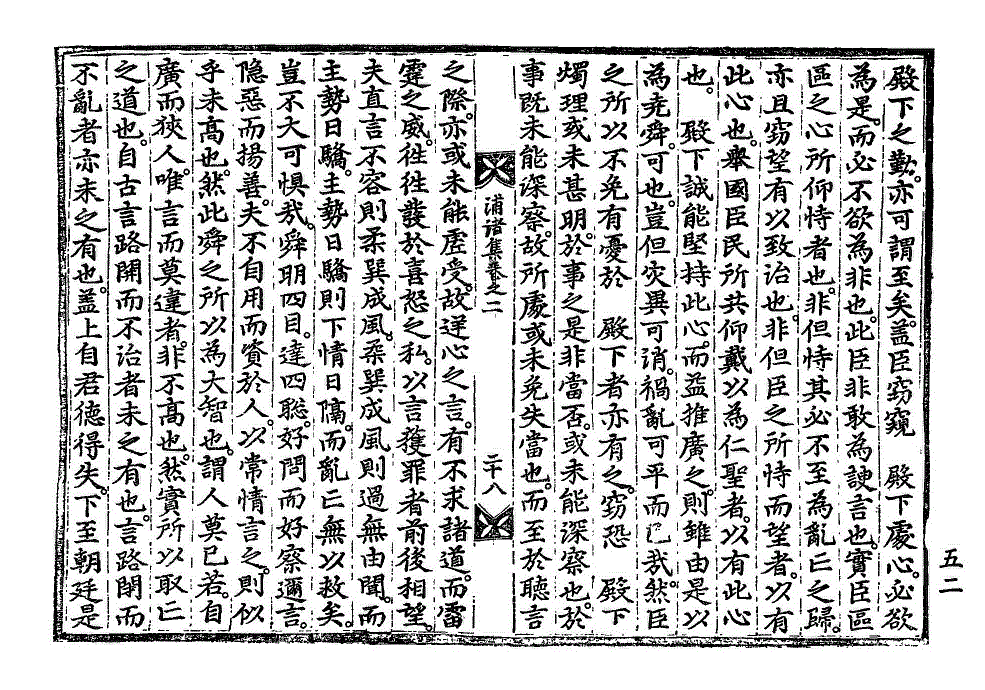 殿下之勤。亦可谓至矣。盖臣窃窥 殿下处心。必欲为是。而必不欲为非也。此臣非敢为谀言也。实臣区区之心所仰恃者也。非但恃其必不至为乱亡之归。亦且窃望有以致治也。非但臣之所恃而望者。以有此心也。举国臣民所共仰戴以为仁圣者。以有此心也。 殿下诚能坚持此心。而益推广之。则虽由是以为尧舜。可也。岂但灾异可消。祸乱可平而已哉。然臣之所以不免有忧于 殿下者亦有之。窃恐 殿下烛理或未甚明。于事之是非当否。或未能深察也。于事既未能深察。故所处或未免失当也。而至于听言之际。亦或未能虚受。故逆心之言。有不求诸道。而雷霆之威。往往发于喜怒之私。以言获罪者前后相望。夫直言不容则柔巽成风。柔巽成风则过无由闻。而主势日骄。主势日骄则下情日隔。而乱亡无以救矣。岂不大可惧哉。舜明四目。达四聪。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夫不自用而资于人。以常情言之。则似乎未高也。然此舜之所以为大智也。谓人莫己若。自广而狭人。唯言而莫违者。非不高也。然实所以取亡之道也。自古言路开而不治者未之有也。言路闭而不乱者亦未之有也。盖上自君德得失。下至朝廷是
殿下之勤。亦可谓至矣。盖臣窃窥 殿下处心。必欲为是。而必不欲为非也。此臣非敢为谀言也。实臣区区之心所仰恃者也。非但恃其必不至为乱亡之归。亦且窃望有以致治也。非但臣之所恃而望者。以有此心也。举国臣民所共仰戴以为仁圣者。以有此心也。 殿下诚能坚持此心。而益推广之。则虽由是以为尧舜。可也。岂但灾异可消。祸乱可平而已哉。然臣之所以不免有忧于 殿下者亦有之。窃恐 殿下烛理或未甚明。于事之是非当否。或未能深察也。于事既未能深察。故所处或未免失当也。而至于听言之际。亦或未能虚受。故逆心之言。有不求诸道。而雷霆之威。往往发于喜怒之私。以言获罪者前后相望。夫直言不容则柔巽成风。柔巽成风则过无由闻。而主势日骄。主势日骄则下情日隔。而乱亡无以救矣。岂不大可惧哉。舜明四目。达四聪。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夫不自用而资于人。以常情言之。则似乎未高也。然此舜之所以为大智也。谓人莫己若。自广而狭人。唯言而莫违者。非不高也。然实所以取亡之道也。自古言路开而不治者未之有也。言路闭而不乱者亦未之有也。盖上自君德得失。下至朝廷是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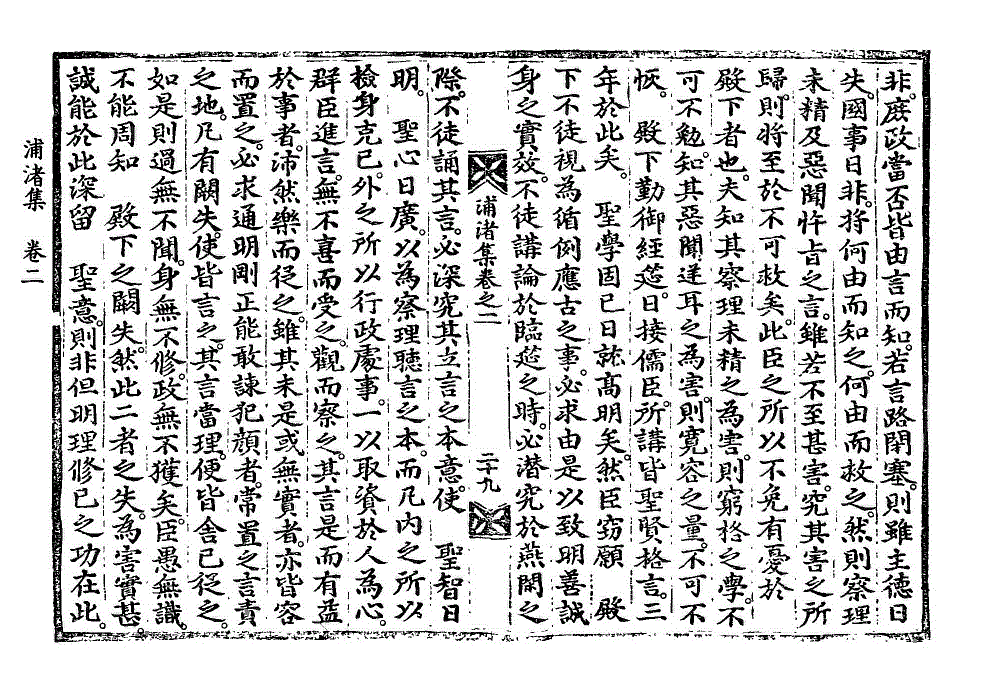 非。庶政当否。皆由言而知。若言路闭塞。则虽主德日失。国事日非。将何由而知之。何由而救之。然则察理未精及恶闻忤旨之言。虽若不至甚害。究其害之所归。则将至于不可救矣。此臣之所以不免有忧于 殿下者也。夫知其察理未精之为害。则穷格之学。不可不勉。知其恶闻逆耳之为害。则宽容之量。不可不恢。 殿下勤御经筵。日接儒臣。所讲皆圣贤格言。三年于此矣。 圣学固已日就高明矣。然臣窃愿 殿下不徒视为循例应古之事。必求由是以致明善诚身之实效。不徒讲论于临筵之时。必潜究于燕闲之际。不徒诵其言。必深究其立言之本意。使 圣智日明。 圣心日广。以为察理听言之本。而凡内之所以检身克己。外之所以行政处事。一以取资于人为心。群臣进言。无不喜而受之。观而察之。其言是而有益于事者。沛然乐而从之。虽其未是或无实者。亦皆容而置之。必求通明刚正能敢谏犯颜者。常置之言责之地。凡有阙失。使皆言之。其言当理。便皆舍己从之。如是则过无不闻。身无不修。政无不获矣。臣愚无识。不能周知 殿下之阙失。然此二者之失。为害实甚。诚能于此深留 圣意。则非但明理修己之功在此。
非。庶政当否。皆由言而知。若言路闭塞。则虽主德日失。国事日非。将何由而知之。何由而救之。然则察理未精及恶闻忤旨之言。虽若不至甚害。究其害之所归。则将至于不可救矣。此臣之所以不免有忧于 殿下者也。夫知其察理未精之为害。则穷格之学。不可不勉。知其恶闻逆耳之为害。则宽容之量。不可不恢。 殿下勤御经筵。日接儒臣。所讲皆圣贤格言。三年于此矣。 圣学固已日就高明矣。然臣窃愿 殿下不徒视为循例应古之事。必求由是以致明善诚身之实效。不徒讲论于临筵之时。必潜究于燕闲之际。不徒诵其言。必深究其立言之本意。使 圣智日明。 圣心日广。以为察理听言之本。而凡内之所以检身克己。外之所以行政处事。一以取资于人为心。群臣进言。无不喜而受之。观而察之。其言是而有益于事者。沛然乐而从之。虽其未是或无实者。亦皆容而置之。必求通明刚正能敢谏犯颜者。常置之言责之地。凡有阙失。使皆言之。其言当理。便皆舍己从之。如是则过无不闻。身无不修。政无不获矣。臣愚无识。不能周知 殿下之阙失。然此二者之失。为害实甚。诚能于此深留 圣意。则非但明理修己之功在此。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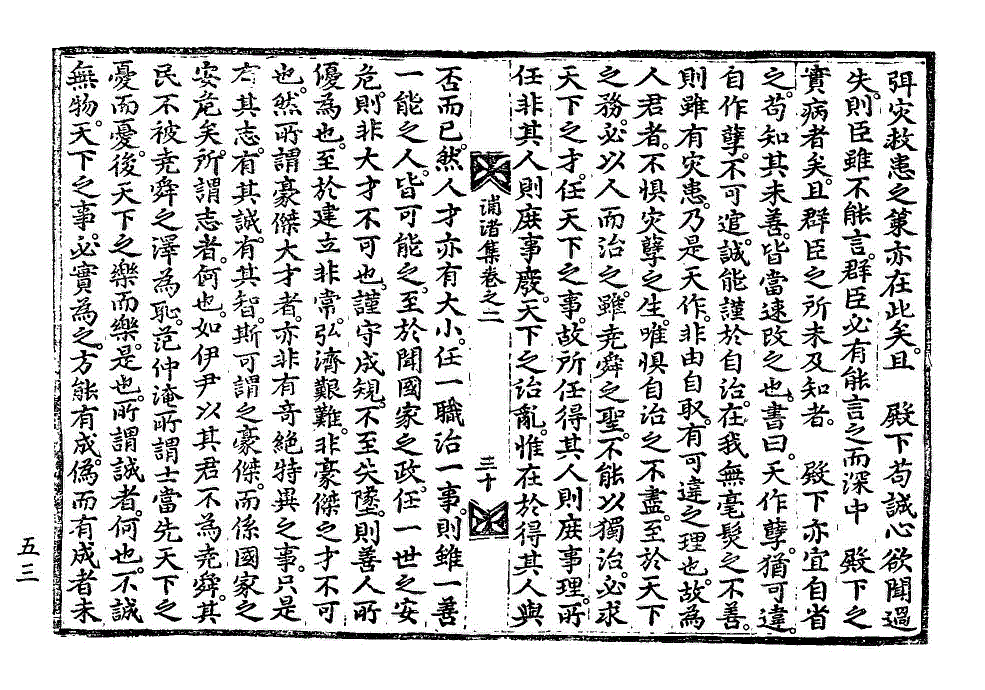 弭灾救患之策亦在此矣。且 殿下苟诚心欲闻过失。则臣虽不能言。群臣必有能言之而深中 殿下之实病者矣。且群臣之所未及知者。 殿下亦宜自省之。苟知其未善。皆当速改之也。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诚能谨于自治。在我无毫发之不善。则虽有灾患。乃是天作。非由自取。有可违之理也。故为人君者。不惧灾孽之生。唯惧自治之不尽。至于天下之务。必以人而治之。虽尧舜之圣。不能以独治。必求天下之才。任天下之事。故所任得其人则庶事理。所任非其人则庶事废。天下之治乱。惟在于得其人与否而已。然人才亦有大小。任一职治一事。则虽一善一能之人。皆可能之。至于闻国家之政。任一世之安危。则非大才不可也。谨守成规。不至失坠。则善人所优为也。至于建立非常。弘济艰难。非豪杰之才不可也。然所谓豪杰大才者。亦非有奇绝特异之事。只是有其志。有其诚。有其智。斯可谓之豪杰。而系国家之安危矣。所谓志者。何也。如伊尹以其君不为尧舜。其民不被尧舜之泽为耻。范仲淹所谓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也。所谓诚者。何也。不诚无物。天下之事。必实为之。方能有成。伪而有成者未
弭灾救患之策亦在此矣。且 殿下苟诚心欲闻过失。则臣虽不能言。群臣必有能言之而深中 殿下之实病者矣。且群臣之所未及知者。 殿下亦宜自省之。苟知其未善。皆当速改之也。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诚能谨于自治。在我无毫发之不善。则虽有灾患。乃是天作。非由自取。有可违之理也。故为人君者。不惧灾孽之生。唯惧自治之不尽。至于天下之务。必以人而治之。虽尧舜之圣。不能以独治。必求天下之才。任天下之事。故所任得其人则庶事理。所任非其人则庶事废。天下之治乱。惟在于得其人与否而已。然人才亦有大小。任一职治一事。则虽一善一能之人。皆可能之。至于闻国家之政。任一世之安危。则非大才不可也。谨守成规。不至失坠。则善人所优为也。至于建立非常。弘济艰难。非豪杰之才不可也。然所谓豪杰大才者。亦非有奇绝特异之事。只是有其志。有其诚。有其智。斯可谓之豪杰。而系国家之安危矣。所谓志者。何也。如伊尹以其君不为尧舜。其民不被尧舜之泽为耻。范仲淹所谓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也。所谓诚者。何也。不诚无物。天下之事。必实为之。方能有成。伪而有成者未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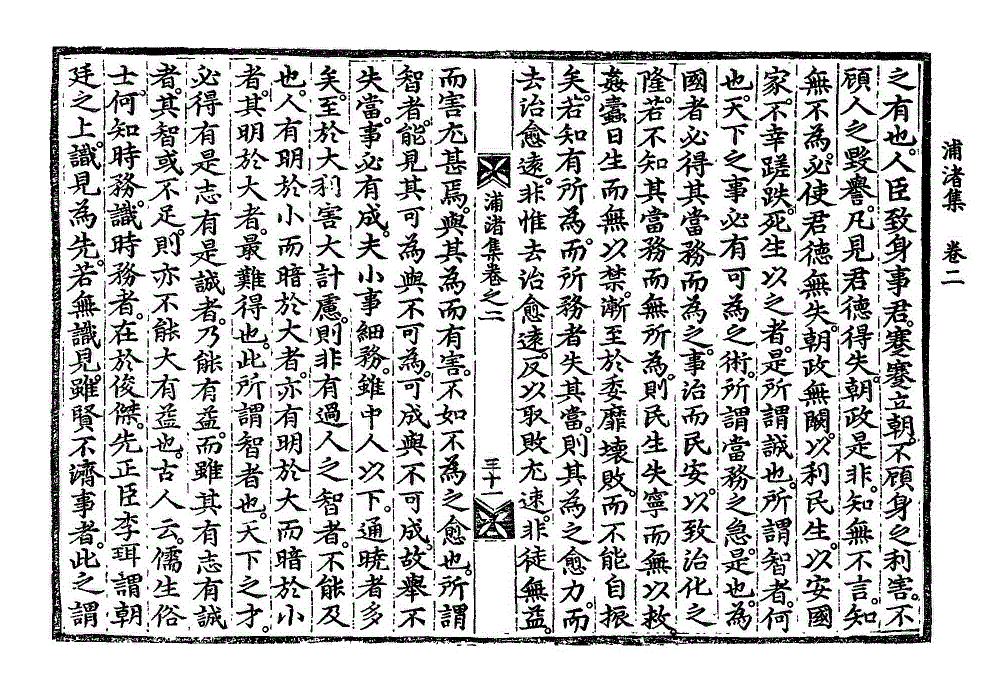 之有也。人臣致身事君。蹇蹇立朝。不顾身之利害。不顾人之毁誉。凡见君德得失。朝政是非。知无不言。知无不为。必使君德无失。朝政无阙。以利民生。以安国家。不幸蹉跌。死生以之者。是所谓诚也。所谓智者。何也。天下之事必有可为之术。所谓当务之急。是也。为国者必得其当务而为之。事治而民安。以致治化之隆。若不知其当务而无所为。则民生失宁而无以救。奸蠹日生而无以禁。渐至于委靡坏败。而不能自振矣。若知有所为。而所务者失其当。则其为之愈力。而去治愈远。非惟去治愈远。反以取败尤速。非徒无益。而害尤甚焉。与其为而有害。不如不为之愈也。所谓智者。能见其可为与不可为。可成与不可成。故举不失当。事必有成。夫小事细务。虽中人以下。通晓者多矣。至于大利害大计虑。则非有过人之智者。不能及也。人有明于小而暗于大者。亦有明于大而暗于小者。其明于大者。最难得也。此所谓智者也。天下之才。必得有是志有是诚者。乃能有益。而虽其有志有诚者。其智或不足。则亦不能大有益也。古人云。儒生俗士。何知时务。识时务者。在于俊杰。先正臣李珥谓朝廷之上。识见为先。若无识见。虽贤不济事者。此之谓
之有也。人臣致身事君。蹇蹇立朝。不顾身之利害。不顾人之毁誉。凡见君德得失。朝政是非。知无不言。知无不为。必使君德无失。朝政无阙。以利民生。以安国家。不幸蹉跌。死生以之者。是所谓诚也。所谓智者。何也。天下之事必有可为之术。所谓当务之急。是也。为国者必得其当务而为之。事治而民安。以致治化之隆。若不知其当务而无所为。则民生失宁而无以救。奸蠹日生而无以禁。渐至于委靡坏败。而不能自振矣。若知有所为。而所务者失其当。则其为之愈力。而去治愈远。非惟去治愈远。反以取败尤速。非徒无益。而害尤甚焉。与其为而有害。不如不为之愈也。所谓智者。能见其可为与不可为。可成与不可成。故举不失当。事必有成。夫小事细务。虽中人以下。通晓者多矣。至于大利害大计虑。则非有过人之智者。不能及也。人有明于小而暗于大者。亦有明于大而暗于小者。其明于大者。最难得也。此所谓智者也。天下之才。必得有是志有是诚者。乃能有益。而虽其有志有诚者。其智或不足。则亦不能大有益也。古人云。儒生俗士。何知时务。识时务者。在于俊杰。先正臣李珥谓朝廷之上。识见为先。若无识见。虽贤不济事者。此之谓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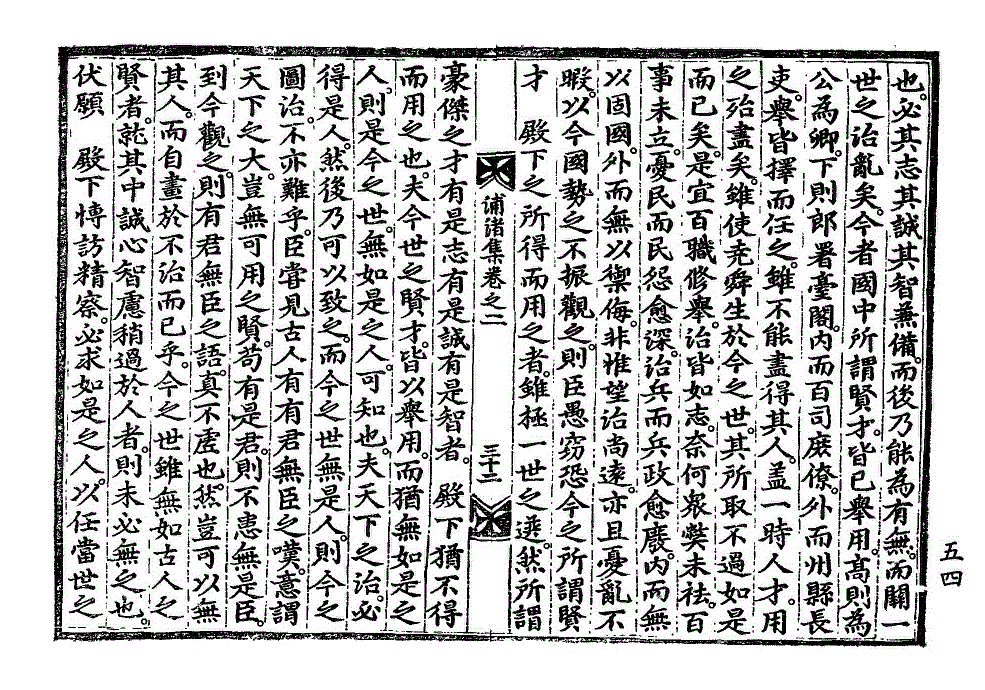 也。必其志其诚其智兼备。而后乃能为有无。而关一世之治乱矣。今者国中所谓贤才。皆已举用。高则为公为卿。下则郎署台阁。内而百司庶僚。外而州县长吏。举皆择而任之。虽不能尽得其人。盖一时人才。用之殆尽矣。虽使尧舜生于今之世。其所取不过如是而已矣。是宜百职修举。治皆如志。奈何众弊未祛。百事未立。忧民而民怨愈深。治兵而兵政愈废。内而无以固国。外而无以御侮。非惟望治尚远。亦且忧乱不暇。以今国势之不振观之。则臣愚窃恐今之所谓贤才 殿下之所得而用之者。虽极一世之选。然所谓豪杰之才有是志有是诚有是智者。 殿下犹不得而用之也。夫今世之贤才。皆以举用。而犹无如是之人。则是今之世。无如是之人。可知也。夫天下之治。必得是人。然后乃可以致之。而今之世无是人。则今之图治。不亦难乎。臣尝见古人有有君无臣之叹。意谓天下之大。岂无可用之贤。苟有是君。则不患无是臣。到今观之。则有君无臣之语。真不虚也。然岂可以无其人。而自画于不治而已乎。今之世虽无如古人之贤者。就其中诚心智虑稍过于人者。则未必无之也。伏愿 殿下博访精察。必求如是之人。以任当世之
也。必其志其诚其智兼备。而后乃能为有无。而关一世之治乱矣。今者国中所谓贤才。皆已举用。高则为公为卿。下则郎署台阁。内而百司庶僚。外而州县长吏。举皆择而任之。虽不能尽得其人。盖一时人才。用之殆尽矣。虽使尧舜生于今之世。其所取不过如是而已矣。是宜百职修举。治皆如志。奈何众弊未祛。百事未立。忧民而民怨愈深。治兵而兵政愈废。内而无以固国。外而无以御侮。非惟望治尚远。亦且忧乱不暇。以今国势之不振观之。则臣愚窃恐今之所谓贤才 殿下之所得而用之者。虽极一世之选。然所谓豪杰之才有是志有是诚有是智者。 殿下犹不得而用之也。夫今世之贤才。皆以举用。而犹无如是之人。则是今之世。无如是之人。可知也。夫天下之治。必得是人。然后乃可以致之。而今之世无是人。则今之图治。不亦难乎。臣尝见古人有有君无臣之叹。意谓天下之大。岂无可用之贤。苟有是君。则不患无是臣。到今观之。则有君无臣之语。真不虚也。然岂可以无其人。而自画于不治而已乎。今之世虽无如古人之贤者。就其中诚心智虑稍过于人者。则未必无之也。伏愿 殿下博访精察。必求如是之人。以任当世之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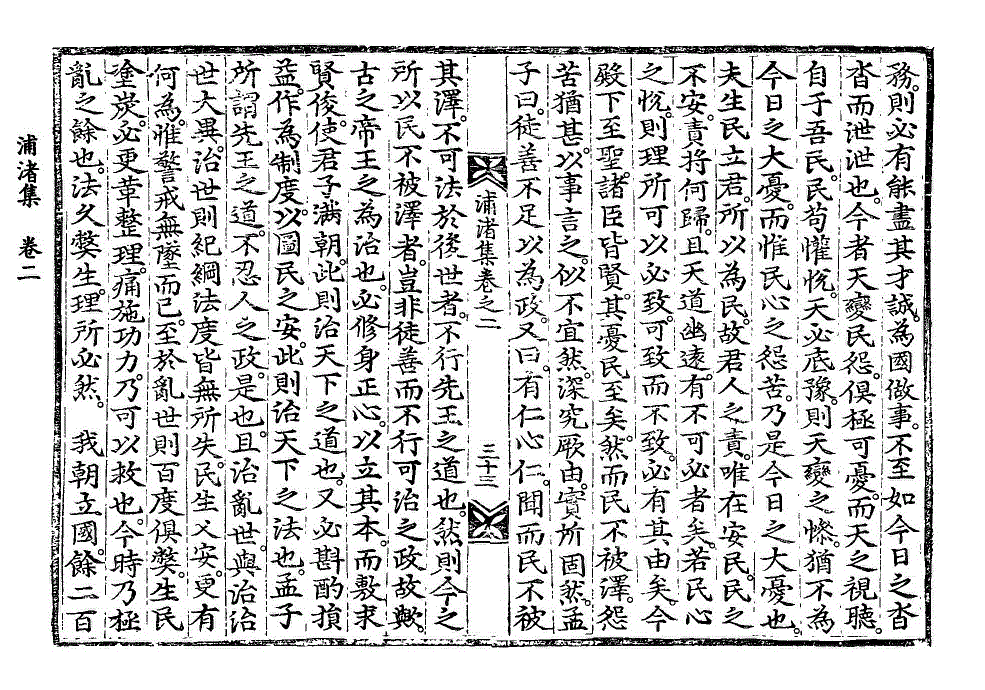 务。则必有能尽其才诚。为国做事。不至如今日之沓沓而泄泄也。今者天变民怨。俱极可忧。而天之视听。自子吾民。民苟欢悦。天必底豫。则天变之惨。犹不为今日之大忧。而惟民心之怨苦。乃是今日之大忧也。夫生民立君。所以为民。故君人之责。唯在安民。民之不安。责将何归。且天道幽远。有不可必者矣。若民心之悦。则理所可以必致。可致而不致。必有其由矣。今殿下至圣。诸臣皆贤。其忧民至矣。然而民不被泽。怨苦犹甚。以事言之。似不宜然。深究厥由。实所固然。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又曰。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然则今之所以民不被泽者。岂非徒善而不行可治之政故欤。古之帝王之为治也。必修身正心。以立其本。而敷求贤俊。君使子满朝。此则治天下之道也。又必斟酌损益。作为制度。以图民之安。此则治天下之法也。孟子所谓先王之道。不忍人之政。是也。且治乱世。与治治世大异。治世则纪纲法度皆无所失。民生又安。更有何为。惟警戒无坠而已。至于乱世则百度俱弊。生民涂炭。必更革整理。痛施功力。乃可以救也。今时乃极乱之馀也。法久弊生。理所必然。 我朝立国。馀二百
务。则必有能尽其才诚。为国做事。不至如今日之沓沓而泄泄也。今者天变民怨。俱极可忧。而天之视听。自子吾民。民苟欢悦。天必底豫。则天变之惨。犹不为今日之大忧。而惟民心之怨苦。乃是今日之大忧也。夫生民立君。所以为民。故君人之责。唯在安民。民之不安。责将何归。且天道幽远。有不可必者矣。若民心之悦。则理所可以必致。可致而不致。必有其由矣。今殿下至圣。诸臣皆贤。其忧民至矣。然而民不被泽。怨苦犹甚。以事言之。似不宜然。深究厥由。实所固然。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又曰。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然则今之所以民不被泽者。岂非徒善而不行可治之政故欤。古之帝王之为治也。必修身正心。以立其本。而敷求贤俊。君使子满朝。此则治天下之道也。又必斟酌损益。作为制度。以图民之安。此则治天下之法也。孟子所谓先王之道。不忍人之政。是也。且治乱世。与治治世大异。治世则纪纲法度皆无所失。民生又安。更有何为。惟警戒无坠而已。至于乱世则百度俱弊。生民涂炭。必更革整理。痛施功力。乃可以救也。今时乃极乱之馀也。法久弊生。理所必然。 我朝立国。馀二百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55L 页
 年。中间政失者屡。弊随而生。因循滋甚。自 宣祖朝。识者犹忧弊政之不改。及经倭难板荡。庶事姑息。至于废朝。坏乱极矣。则生民在水火之中固久矣。然则今之所循以为法制者。皆是病民之积弊也。为今之道。惟在大变通大更张。以痛改其弊。乃可以拯民于水火之中也。今 殿下虽至圣。群臣虽皆贤。然只是自检其身。不自为弊而已。至于流来积弊为害于民者。则一皆仍旧。无一改焉。则是救民之政。初未尝为之也。书曰。不虑胡获。不为胡成。夫民在水火之中。未尝救之。而望其自安。不亦难乎。是犹宿疾危笃之人。未尝施针服药。而求病之自去。身之自安也。宁有是理乎。故臣以为今之民困。乃所固然也。夫今兹害民之弊。积渐已久。而极于废朝。则其致弊之由。固非今日 君臣之咎也。若睹其弊深民困至此。而莫之救。则岂非今日君臣之咎也。 反正之初。大臣首建大同之规。是有意于革弊而救民也。民颇悦之。庶有可苏之望。行之一年。竟以浮议罢。中外之民。深以为恨也。夫主昏臣佞。无意于求治者。固无望于救民矣。今殿下不世之主。群臣皆极一世之望。惟日忧勤。无非所以图治也。而积弊不祛。民困莫救。岂非可惜之甚
年。中间政失者屡。弊随而生。因循滋甚。自 宣祖朝。识者犹忧弊政之不改。及经倭难板荡。庶事姑息。至于废朝。坏乱极矣。则生民在水火之中固久矣。然则今之所循以为法制者。皆是病民之积弊也。为今之道。惟在大变通大更张。以痛改其弊。乃可以拯民于水火之中也。今 殿下虽至圣。群臣虽皆贤。然只是自检其身。不自为弊而已。至于流来积弊为害于民者。则一皆仍旧。无一改焉。则是救民之政。初未尝为之也。书曰。不虑胡获。不为胡成。夫民在水火之中。未尝救之。而望其自安。不亦难乎。是犹宿疾危笃之人。未尝施针服药。而求病之自去。身之自安也。宁有是理乎。故臣以为今之民困。乃所固然也。夫今兹害民之弊。积渐已久。而极于废朝。则其致弊之由。固非今日 君臣之咎也。若睹其弊深民困至此。而莫之救。则岂非今日君臣之咎也。 反正之初。大臣首建大同之规。是有意于革弊而救民也。民颇悦之。庶有可苏之望。行之一年。竟以浮议罢。中外之民。深以为恨也。夫主昏臣佞。无意于求治者。固无望于救民矣。今殿下不世之主。群臣皆极一世之望。惟日忧勤。无非所以图治也。而积弊不祛。民困莫救。岂非可惜之甚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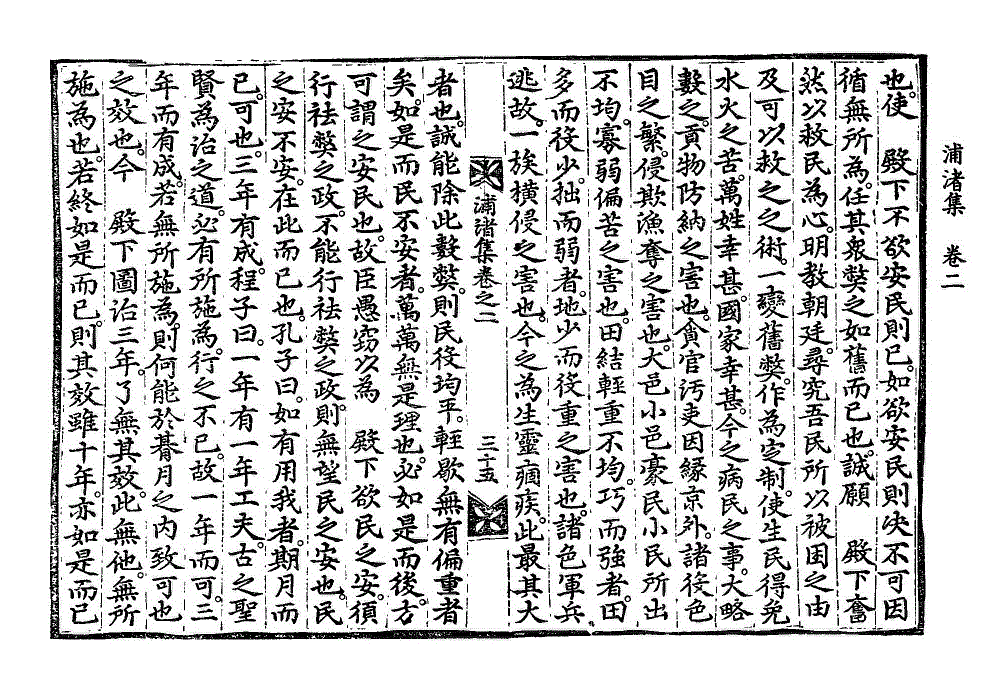 也。使 殿下不欲安民则已。如欲安民则决不可因循无所为。任其众弊之如旧而已也。诚愿 殿下奋然以救民为心。明教朝廷。寻究吾民所以被困之由及可以救之之术。一变旧弊。作为定制。使生民得免水火之苦。万姓幸甚。国家幸甚。今之病民之事。大略数之。贡物防纳之害也。贪官污吏因缘京外。诸役色目之繁。侵欺渔夺之害也。大邑小邑豪民小民所出不均。寡弱偏苦之害也。田结轻重不均。巧而强者。田多而役少。拙而弱者。地少而役重之害也。诸色军兵逃故。一族横侵之害也。今之为生灵痼疾。此最其大者也。诚能除此数弊。则民役均平。轻歇无有偏重者矣。如是而民不安者。万万无是理也。必如是而后。方可谓之安民也。故臣愚窃以为 殿下欲民之安。须行祛弊之政。不能行祛弊之政。则无望民之安也。民之安不安。在此而已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程子曰。一年有一年工夫。古之圣贤为治之道。必有所施为。行之不已。故一年而可。三年而有成。若无所施为。则何能于期月之内致可也之效也。今 殿下图治三年。了无其效。此无他。无所施为也。若终如是而已。则其效虽十年。亦如是而已
也。使 殿下不欲安民则已。如欲安民则决不可因循无所为。任其众弊之如旧而已也。诚愿 殿下奋然以救民为心。明教朝廷。寻究吾民所以被困之由及可以救之之术。一变旧弊。作为定制。使生民得免水火之苦。万姓幸甚。国家幸甚。今之病民之事。大略数之。贡物防纳之害也。贪官污吏因缘京外。诸役色目之繁。侵欺渔夺之害也。大邑小邑豪民小民所出不均。寡弱偏苦之害也。田结轻重不均。巧而强者。田多而役少。拙而弱者。地少而役重之害也。诸色军兵逃故。一族横侵之害也。今之为生灵痼疾。此最其大者也。诚能除此数弊。则民役均平。轻歇无有偏重者矣。如是而民不安者。万万无是理也。必如是而后。方可谓之安民也。故臣愚窃以为 殿下欲民之安。须行祛弊之政。不能行祛弊之政。则无望民之安也。民之安不安。在此而已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程子曰。一年有一年工夫。古之圣贤为治之道。必有所施为。行之不已。故一年而可。三年而有成。若无所施为。则何能于期月之内致可也之效也。今 殿下图治三年。了无其效。此无他。无所施为也。若终如是而已。则其效虽十年。亦如是而已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56L 页
 也。且既不能有进。则窃恐其将陵夷坏败益甚。又不止如今日也。至于号牌之法则臣窃疑之。夫此法之行。本欲充逃故之阙。除族邻之侵。是亦所以祛弊而救民也。其意岂不善哉。然近见人自外方来者。皆言以号牌之故。民间极扰。怨讟盈路。愚顽之民。不呈单子。移去者极多。虽其呈单子者。率多伪冒。臣窃以为可虑也。臣请详论号牌得失也。夫号牌。本古所未有。至 皇朝始有之。然只朝官佩之。庶民则不佩也。今之号牌。与 皇朝异。所以括民数使不得漏。而又使不得任意移徙也。夫括出无遗。则民皆定役。无不役者矣。不得移徙。则定役者无逃避之路矣。此号牌之利也。然其括民无漏则可也。使不得移徙则不可也。夫民之为性。莫不喜安居而苦羁旅。使得安于田里。生业有恒。更无所苦。则必不舍而移去矣。其去者。必其生业已尽。困苦不堪者也。故王者之治。只要保存其民。使无所苦。则自不移去矣。未闻设法以禁亡者也。盖民苟被苦。至不可堪。则唯有流亡。乃是生道。既不能使民不至于此极。而又禁之使不得去。则是杀之而已。岂仁人之所忍哉。如使王者之政当禁民去。则孔孟必言其宜禁也。孔孟之言。惟以上不恤民。使
也。且既不能有进。则窃恐其将陵夷坏败益甚。又不止如今日也。至于号牌之法则臣窃疑之。夫此法之行。本欲充逃故之阙。除族邻之侵。是亦所以祛弊而救民也。其意岂不善哉。然近见人自外方来者。皆言以号牌之故。民间极扰。怨讟盈路。愚顽之民。不呈单子。移去者极多。虽其呈单子者。率多伪冒。臣窃以为可虑也。臣请详论号牌得失也。夫号牌。本古所未有。至 皇朝始有之。然只朝官佩之。庶民则不佩也。今之号牌。与 皇朝异。所以括民数使不得漏。而又使不得任意移徙也。夫括出无遗。则民皆定役。无不役者矣。不得移徙。则定役者无逃避之路矣。此号牌之利也。然其括民无漏则可也。使不得移徙则不可也。夫民之为性。莫不喜安居而苦羁旅。使得安于田里。生业有恒。更无所苦。则必不舍而移去矣。其去者。必其生业已尽。困苦不堪者也。故王者之治。只要保存其民。使无所苦。则自不移去矣。未闻设法以禁亡者也。盖民苟被苦。至不可堪。则唯有流亡。乃是生道。既不能使民不至于此极。而又禁之使不得去。则是杀之而已。岂仁人之所忍哉。如使王者之政当禁民去。则孔孟必言其宜禁也。孔孟之言。惟以上不恤民。使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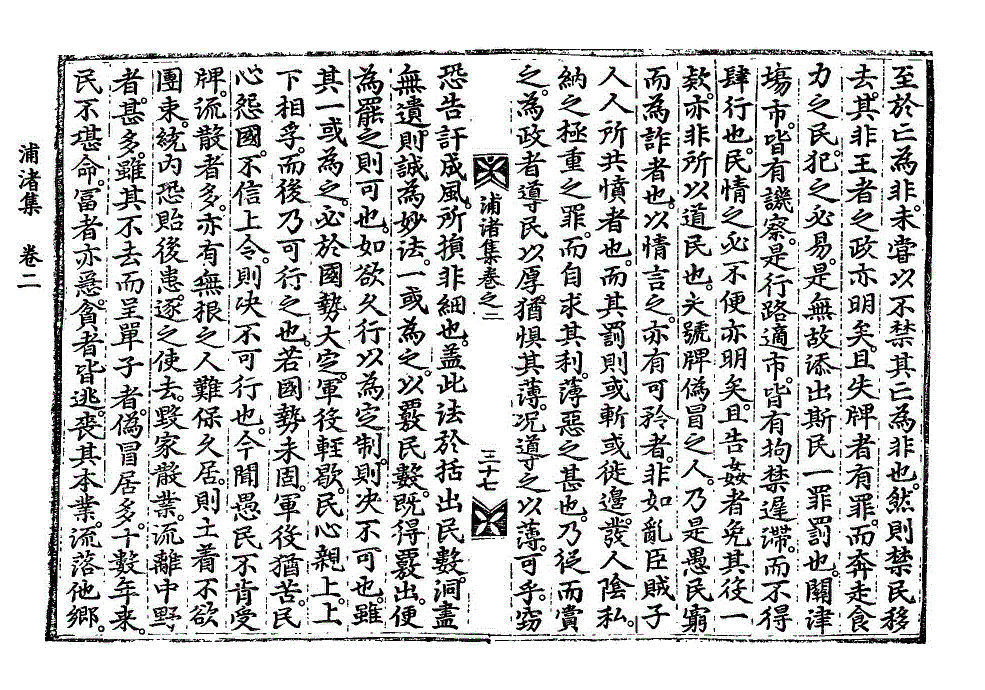 至于亡为非。未尝以不禁其亡为非也。然则禁民移去。其非王者之政亦明矣。且失牌者有罪。而奔走食力之民。犯之必易。是无故添出斯民一罪罚也。关津场市。皆有讥察。是行路适市。皆有拘禁迟滞。而不得肆行也。民情之必不便亦明矣。且告奸者免其役一款。亦非所以道民也。夫号牌伪冒之人。乃是愚民穷而为诈者也。以情言之。亦有可矜者。非如乱臣贼子人人所共愤者也。而其罚则或斩或徙边。发人阴私。纳之极重之罪。而自求其利。薄恶之甚也。乃从而赏之。为政者导民以厚。犹惧其薄。况导之以薄。可乎。窃恐告讦成风。所损非细也。盖此法于括出民数。洞尽无遗。则诚为妙法。一或为之。以覈民数。既得覈出。便为罢之则可也。如欲久行以为定制。则决不可也。虽其一或为之。必于国势大定。军役轻歇。民心亲上。上下相孚。而后乃可行之也。若国势未固。军役犹苦。民心怨国。不信上令。则决不可行也。今闻愚民不肯受牌。流散者多。亦有无根之人难保久居。则土着不欲团束。统内恐贻后患。逐之使去。毁家散业。流离中野者。甚多。虽其不去而呈单子者。伪冒居多。十数年来。民不堪命。富者亦急。贫者皆逃。丧其本业。流落他乡。
至于亡为非。未尝以不禁其亡为非也。然则禁民移去。其非王者之政亦明矣。且失牌者有罪。而奔走食力之民。犯之必易。是无故添出斯民一罪罚也。关津场市。皆有讥察。是行路适市。皆有拘禁迟滞。而不得肆行也。民情之必不便亦明矣。且告奸者免其役一款。亦非所以道民也。夫号牌伪冒之人。乃是愚民穷而为诈者也。以情言之。亦有可矜者。非如乱臣贼子人人所共愤者也。而其罚则或斩或徙边。发人阴私。纳之极重之罪。而自求其利。薄恶之甚也。乃从而赏之。为政者导民以厚。犹惧其薄。况导之以薄。可乎。窃恐告讦成风。所损非细也。盖此法于括出民数。洞尽无遗。则诚为妙法。一或为之。以覈民数。既得覈出。便为罢之则可也。如欲久行以为定制。则决不可也。虽其一或为之。必于国势大定。军役轻歇。民心亲上。上下相孚。而后乃可行之也。若国势未固。军役犹苦。民心怨国。不信上令。则决不可行也。今闻愚民不肯受牌。流散者多。亦有无根之人难保久居。则土着不欲团束。统内恐贻后患。逐之使去。毁家散业。流离中野者。甚多。虽其不去而呈单子者。伪冒居多。十数年来。民不堪命。富者亦急。贫者皆逃。丧其本业。流落他乡。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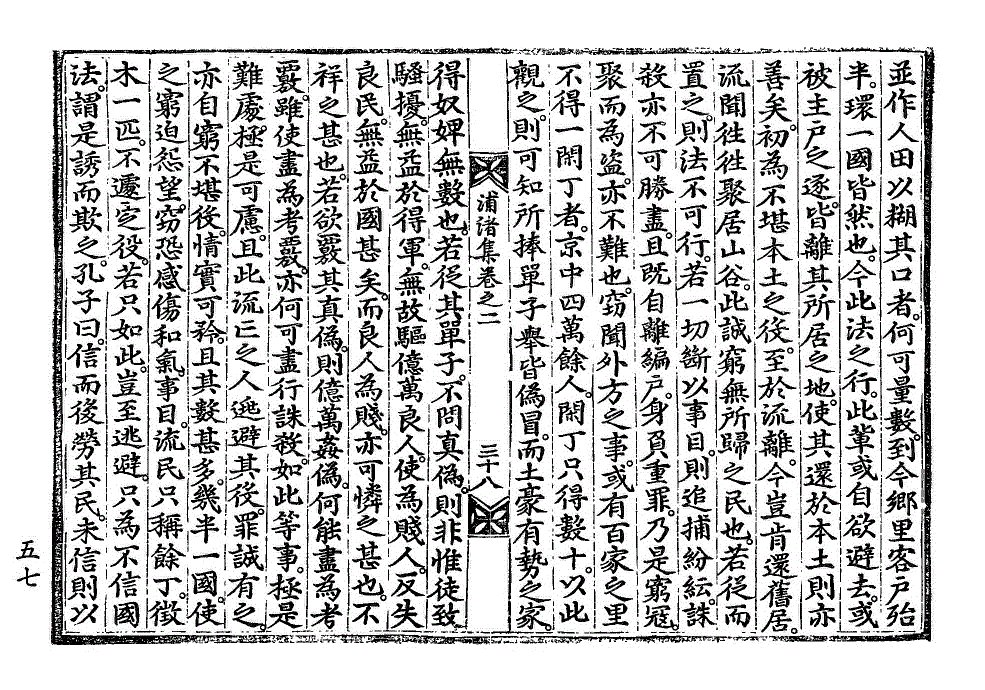 并作人田以糊其口者。何可量数。到今乡里客户殆半。环一国皆然也。今此法之行。此辈或自欲避去。或被主户之逐。皆离其所居之地。使其还于本土则亦善矣。初为不堪本土之役。至于流离。今岂肯还旧居。流闻往往聚居山谷。此诚穷无所归之民也。若从而置之。则法不可行。若一切断以事目。则追捕纷纭。诛杀亦不可胜尽。且既自离编户。身负重罪。乃是穷寇。聚而为盗。亦不难也。窃闻外方之事。或有百家之里不得一闲丁者。京中四万馀人。闲丁只得数十。以此观之。则可知所捧单子举皆伪冒。而土豪有势之家。得奴婢无数也。若从其单子。不问真伪。则非惟徒致骚扰。无益于得军。无故驱亿万良人。使为贱人。反失良民。无益于国甚矣。而良人为贱。亦可怜之甚也。不祥之甚也。若欲覈其真伪。则亿万奸伪。何能尽为考覈。虽使尽为考覈。亦何可尽行诛杀。如此等事。极是难处。极是可虑。且此流亡之人逃避其役。罪诚有之。亦自穷不堪役。情实可矜。且其数甚多。几半一国。使之穷迫怨望。窃恐感伤和气。事目。流民只称馀丁。徵木一匹。不遽定役。若只如此。岂至逃避。只为不信国法。谓是诱而欺之。孔子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
并作人田以糊其口者。何可量数。到今乡里客户殆半。环一国皆然也。今此法之行。此辈或自欲避去。或被主户之逐。皆离其所居之地。使其还于本土则亦善矣。初为不堪本土之役。至于流离。今岂肯还旧居。流闻往往聚居山谷。此诚穷无所归之民也。若从而置之。则法不可行。若一切断以事目。则追捕纷纭。诛杀亦不可胜尽。且既自离编户。身负重罪。乃是穷寇。聚而为盗。亦不难也。窃闻外方之事。或有百家之里不得一闲丁者。京中四万馀人。闲丁只得数十。以此观之。则可知所捧单子举皆伪冒。而土豪有势之家。得奴婢无数也。若从其单子。不问真伪。则非惟徒致骚扰。无益于得军。无故驱亿万良人。使为贱人。反失良民。无益于国甚矣。而良人为贱。亦可怜之甚也。不祥之甚也。若欲覈其真伪。则亿万奸伪。何能尽为考覈。虽使尽为考覈。亦何可尽行诛杀。如此等事。极是难处。极是可虑。且此流亡之人逃避其役。罪诚有之。亦自穷不堪役。情实可矜。且其数甚多。几半一国。使之穷迫怨望。窃恐感伤和气。事目。流民只称馀丁。徵木一匹。不遽定役。若只如此。岂至逃避。只为不信国法。谓是诱而欺之。孔子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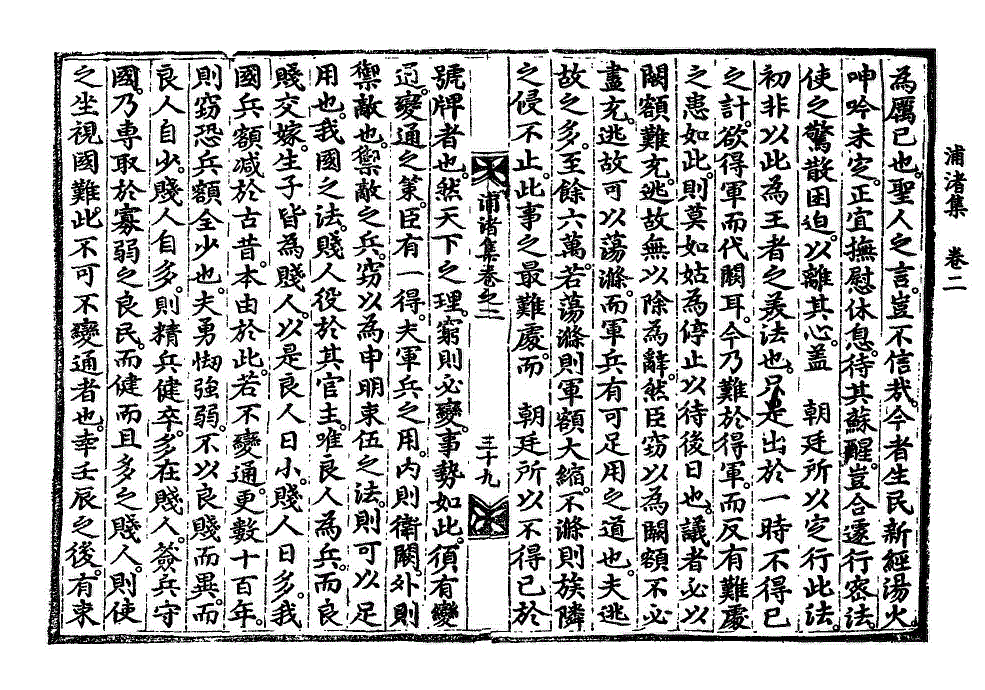 为厉己也。圣人之言。岂不信哉。今者生民新经汤火。呻吟未定。正宜抚慰休息。待其苏醒。岂合遽行密法。使之惊散困迫。以离其心。盖 朝廷所以定行此法。初非以此为王者之美法也。只是出于一时不得已之计。欲得军而代阙耳。今乃难于得军。而反有难处之患如此。则莫如姑为停止以待后日也。议者必以阙额难充。逃故无以除为辞。然臣窃以为阙额不必尽充。逃故可以荡涤。而军兵有可足用之道也。夫逃故之多。至馀六万。若荡涤则军额大缩。不涤则族邻之侵不止。此事之最难处。而 朝廷所以不得已于号牌者也。然天下之理。穷则必变。事势如此。须有变通。变通之策。臣有一得。夫军兵之用。内则卫阙。外则御敌也。御敌之兵。窃以为申明束伍之法。则可以足用也。我国之法。贱人役于其官主。唯良人为兵。而良贱交嫁。生子皆为贱人。以是良人日小。贱人日多。我国兵额减于古昔。本由于此。若不变通。更数十百年。则窃恐兵额全少也。夫勇怯强弱。不以良贱而异。而良人自少。贱人自多。则精兵健卒。多在贱人。签兵守国。乃专取于寡弱之良民。而健而且多之贱人。则使之坐视国难。此不可不变通者也。幸壬辰之后。有束
为厉己也。圣人之言。岂不信哉。今者生民新经汤火。呻吟未定。正宜抚慰休息。待其苏醒。岂合遽行密法。使之惊散困迫。以离其心。盖 朝廷所以定行此法。初非以此为王者之美法也。只是出于一时不得已之计。欲得军而代阙耳。今乃难于得军。而反有难处之患如此。则莫如姑为停止以待后日也。议者必以阙额难充。逃故无以除为辞。然臣窃以为阙额不必尽充。逃故可以荡涤。而军兵有可足用之道也。夫逃故之多。至馀六万。若荡涤则军额大缩。不涤则族邻之侵不止。此事之最难处。而 朝廷所以不得已于号牌者也。然天下之理。穷则必变。事势如此。须有变通。变通之策。臣有一得。夫军兵之用。内则卫阙。外则御敌也。御敌之兵。窃以为申明束伍之法。则可以足用也。我国之法。贱人役于其官主。唯良人为兵。而良贱交嫁。生子皆为贱人。以是良人日小。贱人日多。我国兵额减于古昔。本由于此。若不变通。更数十百年。则窃恐兵额全少也。夫勇怯强弱。不以良贱而异。而良人自少。贱人自多。则精兵健卒。多在贱人。签兵守国。乃专取于寡弱之良民。而健而且多之贱人。则使之坐视国难。此不可不变通者也。幸壬辰之后。有束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58L 页
 伍之法。勿论良贱。行之既久。人不为怪。今宜申明此法。使诸道兵使悉力行之。有阙者填补。额少者加抄。蠲其可减之役。俾免本邑之侵。而择定将官。以时鍊习。使皆成材。则皆为可用之兵矣。如是则良兵虽缩。贱兵自足。自不乏于战陈之用矣。至于卫 阙之兵。则臣窃料每番三千名。则分军甚足。一岁六番。大率不过二万而足矣。时存应上番者。计不减于此。虽减于此。若并其保人为正军。则必有馀矣。臣意以为国内男丁。勿论有职无职良人贱人。皆收斗米。则其数必多。时存保率。并为作户。使之上番。而每番给米。如其所徵于保人者。则卫卒之番。自无不足。而停号牌而收米。则人必乐于出米。与平价而送番。则兵必乐于上番矣。如是则中外之兵粗足。而号牌可停。逃故可涤。族邻免侵矣。如此支过数年。观国内粗平。民心安定。而后可更议搜括。以充军额也。此国之大事。所系利害极重。伏愿 殿下勿以臣愚而忽之。深加 睿思。谋及朝廷。如以臣言为可。则早为改之。万姓幸甚。 国家幸甚。当今之事可言者多矣。然而其事细微。非关安危者。臣不必言。今此所陈。皆 国家大计。安危所关。其言 殿下一身所当为者。不举古昔圣
伍之法。勿论良贱。行之既久。人不为怪。今宜申明此法。使诸道兵使悉力行之。有阙者填补。额少者加抄。蠲其可减之役。俾免本邑之侵。而择定将官。以时鍊习。使皆成材。则皆为可用之兵矣。如是则良兵虽缩。贱兵自足。自不乏于战陈之用矣。至于卫 阙之兵。则臣窃料每番三千名。则分军甚足。一岁六番。大率不过二万而足矣。时存应上番者。计不减于此。虽减于此。若并其保人为正军。则必有馀矣。臣意以为国内男丁。勿论有职无职良人贱人。皆收斗米。则其数必多。时存保率。并为作户。使之上番。而每番给米。如其所徵于保人者。则卫卒之番。自无不足。而停号牌而收米。则人必乐于出米。与平价而送番。则兵必乐于上番矣。如是则中外之兵粗足。而号牌可停。逃故可涤。族邻免侵矣。如此支过数年。观国内粗平。民心安定。而后可更议搜括。以充军额也。此国之大事。所系利害极重。伏愿 殿下勿以臣愚而忽之。深加 睿思。谋及朝廷。如以臣言为可。则早为改之。万姓幸甚。 国家幸甚。当今之事可言者多矣。然而其事细微。非关安危者。臣不必言。今此所陈。皆 国家大计。安危所关。其言 殿下一身所当为者。不举古昔圣浦渚先生集卷之二 第 59H 页
 贤治心修身所以去人欲复天理之正法。而只以明理听言为献者。诚以 殿下即位以来。 经席所讲。无非圣贤格言。儒臣进说。无非圣贤成法。其于心法之要。出治之本。闻之熟矣。讲之详矣。而惟理有未明。言不见容。乃是 殿下切己之患。尤不可不知者也。然苟能于此深留 圣意。则治心修身之功。亦不外此矣。所论国事之不振。由于人才之不得。民生之怨苦。由于仁政之不行。亦皆穷本探源。求其所以然之故。必由于此而不可易者也。至于号牌。则乃今日利害之极大者。朝论已定。法令已具。佩牌之期不远。诚不可轻易议之。第见其本非美法。而于今行之。了无所益而生患反大。私窃忧之。顾今朝臣皆谓可行。一人私见。势难枝梧。必知言出而众怒群怪。身且不保也。亦计中外诸臣如臣之见者。多矣。皆以 朝家大计已定。不敢言之耳。然见其可忧如此而不言。则是欺 圣明也。负 国家也。负生民也。故趑趄久之。不敢终默。冒昧陈之。伏愿 圣明矜其愚而察其忱。不胜幸甚。臣无任激切屏营之至。谨昧死以 闻。
贤治心修身所以去人欲复天理之正法。而只以明理听言为献者。诚以 殿下即位以来。 经席所讲。无非圣贤格言。儒臣进说。无非圣贤成法。其于心法之要。出治之本。闻之熟矣。讲之详矣。而惟理有未明。言不见容。乃是 殿下切己之患。尤不可不知者也。然苟能于此深留 圣意。则治心修身之功。亦不外此矣。所论国事之不振。由于人才之不得。民生之怨苦。由于仁政之不行。亦皆穷本探源。求其所以然之故。必由于此而不可易者也。至于号牌。则乃今日利害之极大者。朝论已定。法令已具。佩牌之期不远。诚不可轻易议之。第见其本非美法。而于今行之。了无所益而生患反大。私窃忧之。顾今朝臣皆谓可行。一人私见。势难枝梧。必知言出而众怒群怪。身且不保也。亦计中外诸臣如臣之见者。多矣。皆以 朝家大计已定。不敢言之耳。然见其可忧如此而不言。则是欺 圣明也。负 国家也。负生民也。故趑趄久之。不敢终默。冒昧陈之。伏愿 圣明矜其愚而察其忱。不胜幸甚。臣无任激切屏营之至。谨昧死以 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