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x 页
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志录(下)
志录(下)
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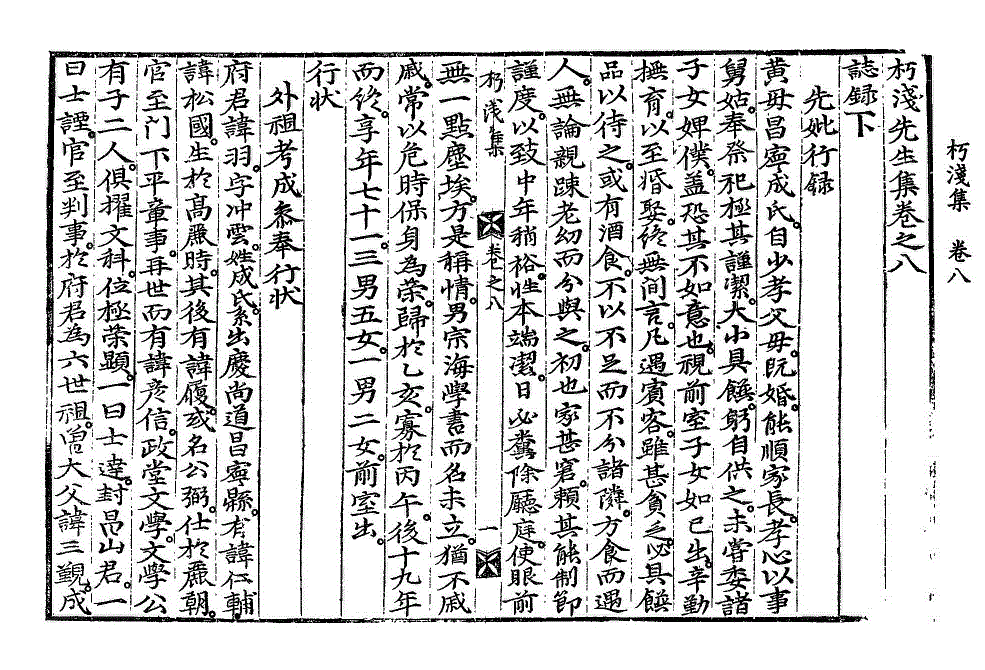 先妣行录
先妣行录黄母昌宁成氏。自少孝父母。既婚。能顺家长。孝心以事舅姑。奉祭祀极其谨洁。大小具馔。躬自供之。未尝委诸子女婢仆。盖恐其不如意也。视前室子女如己出。辛勤抚育。以至婚娶。终无间言。凡遇宾客。虽甚贫乏。必具馔品以待之。或有酒食。不以不足而不分诸邻。方食而遇人。无论亲疏老幼而分与之。初也家甚窘。赖其能制节谨度。以致中年稍裕。性本端洁。日必粪除厅庭。使眼前无一点尘埃。方是称情。男宗海学书而名未立。犹不戚戚。常以危时保身为荣。归于乙亥。寡于丙午。后十九年而终。享年七十一。三男五女。一男二女。前室出。
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行状
外祖考成参奉行状
府君讳羽。字冲云。姓成氏。系出庆尚道昌宁县。有讳仁辅,讳松国。生于高丽时。其后有讳履。或名公弼。仕于丽朝。官至门下平章事。再世而有讳彦信。政堂文学。文学公有子二人。俱擢文科。位极荣显。一曰士达。封昌山君。一曰士諲。官至判事。于府君为六世祖。曾大父讳三觐。成
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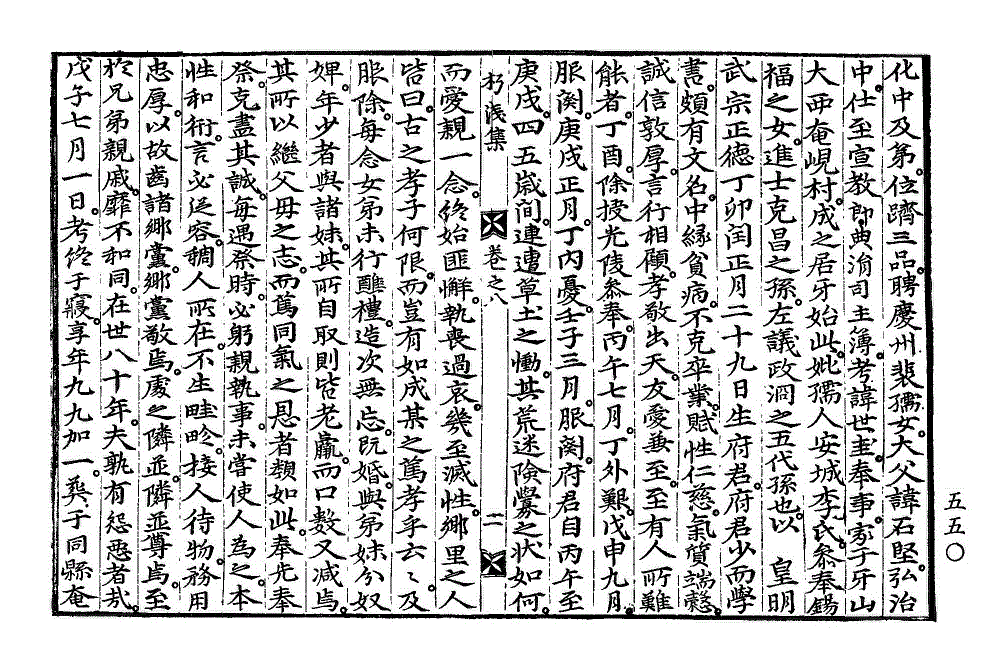 化中及第。位跻三品。聘庆州裴孺女。大父讳石坚。弘治中。仕至宣教郎,典涓司主簿。考讳世圭。奉事。家于牙山大西奄岘村。成之居牙始此。妣孺人安城李氏。参奉锡福之女。进士克昌之孙。左议政浻之五代孙也。以 皇明武宗正德丁卯闰正月二十九日生府君。府君少而学书。颇有文名。中缘贫病。不克卒业。赋性仁慈。气质端悫。诚信敦厚。言行相顾。孝敬出天。友爱兼至。至有人所难能者。丁酉。除授光陵参奉。丙午七月。丁外艰。戊申九月。服阕。庚戌正月。丁内忧。壬子三月。服阕。府君自丙午至庚戌。四五岁间。连遭草土之恸。其荒迷险衅之状如何。而爱亲一念。终始匪懈。执丧过哀。几至灭性。乡里之人皆曰。古之孝子何限。而岂有如成某之笃孝乎云云。及服除。每念女弟未行醮礼。造次无忘。既婚。与弟妹分奴婢。年少者与诸妹。其所自取则皆老羸。而口数又减焉。其所以继父母之志。而笃同气之恩者类如此。奉先奉祭。克尽其诚。每遇祭时。必躬亲执事。未尝使人为之。本性和衎。言必从容。稠人所在。不生畦畛。接人待物。务用忠厚。以故齿诸乡党。乡党敬焉。处之邻并。邻并尊焉。至于兄弟亲戚。靡不和同。在世八十年。夫孰有怨恶者哉。戊子七月一日。考终于寝。享年九九加一。葬于同县奄
化中及第。位跻三品。聘庆州裴孺女。大父讳石坚。弘治中。仕至宣教郎,典涓司主簿。考讳世圭。奉事。家于牙山大西奄岘村。成之居牙始此。妣孺人安城李氏。参奉锡福之女。进士克昌之孙。左议政浻之五代孙也。以 皇明武宗正德丁卯闰正月二十九日生府君。府君少而学书。颇有文名。中缘贫病。不克卒业。赋性仁慈。气质端悫。诚信敦厚。言行相顾。孝敬出天。友爱兼至。至有人所难能者。丁酉。除授光陵参奉。丙午七月。丁外艰。戊申九月。服阕。庚戌正月。丁内忧。壬子三月。服阕。府君自丙午至庚戌。四五岁间。连遭草土之恸。其荒迷险衅之状如何。而爱亲一念。终始匪懈。执丧过哀。几至灭性。乡里之人皆曰。古之孝子何限。而岂有如成某之笃孝乎云云。及服除。每念女弟未行醮礼。造次无忘。既婚。与弟妹分奴婢。年少者与诸妹。其所自取则皆老羸。而口数又减焉。其所以继父母之志。而笃同气之恩者类如此。奉先奉祭。克尽其诚。每遇祭时。必躬亲执事。未尝使人为之。本性和衎。言必从容。稠人所在。不生畦畛。接人待物。务用忠厚。以故齿诸乡党。乡党敬焉。处之邻并。邻并尊焉。至于兄弟亲戚。靡不和同。在世八十年。夫孰有怨恶者哉。戊子七月一日。考终于寝。享年九九加一。葬于同县奄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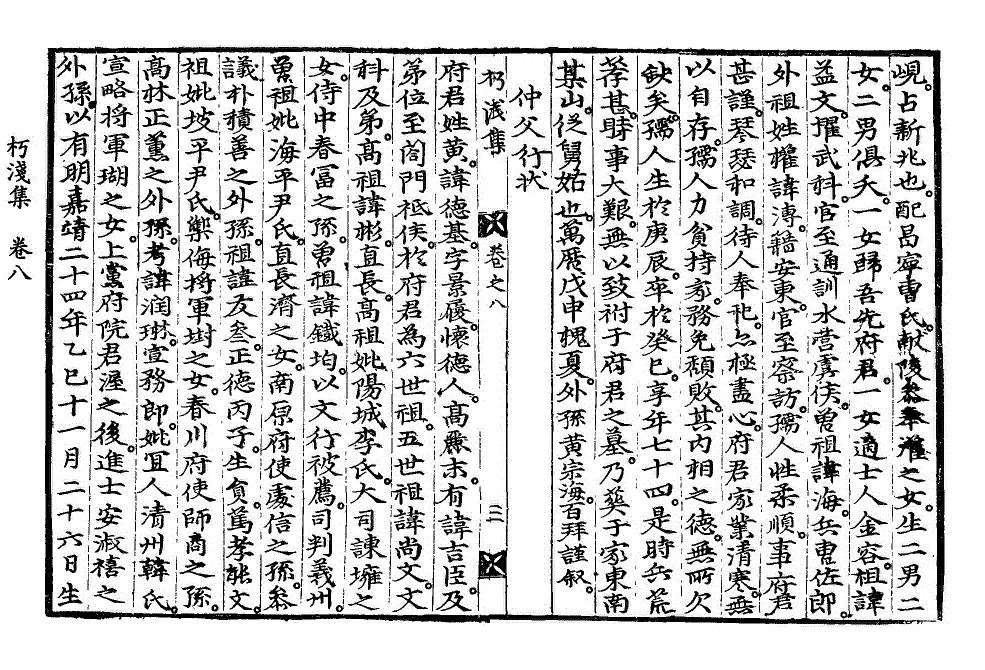 岘。占新兆也。配曷宁曹氏。献陵参奉灌之女。生二男二女。二男俱夭。一女归吾先府君。一女适士人金容。祖讳益文。擢武科。官至通训水营虞侯。曾祖讳海。兵曹佐郎。外祖姓权讳漙。藉安东。官至察访。孺人性柔顺。事府君甚谨。琴瑟和调。待人奉祀。亦极尽心。府君家业清寒。无以自存。孺人力贫持家。务免颓败。其内相之德。无所欠缺矣。孺人生于庚辰。卒于癸巳。享年七十四。是时兵荒荐甚。时事大艰。无以致祔于府君之墓。乃葬于家东南某山。从舅姑也。万历戊申槐夏。外孙黄宗海。百拜谨叙。
岘。占新兆也。配曷宁曹氏。献陵参奉灌之女。生二男二女。二男俱夭。一女归吾先府君。一女适士人金容。祖讳益文。擢武科。官至通训水营虞侯。曾祖讳海。兵曹佐郎。外祖姓权讳漙。藉安东。官至察访。孺人性柔顺。事府君甚谨。琴瑟和调。待人奉祀。亦极尽心。府君家业清寒。无以自存。孺人力贫持家。务免颓败。其内相之德。无所欠缺矣。孺人生于庚辰。卒于癸巳。享年七十四。是时兵荒荐甚。时事大艰。无以致祔于府君之墓。乃葬于家东南某山。从舅姑也。万历戊申槐夏。外孙黄宗海。百拜谨叙。仲父行状
府君姓黄。讳德基。字景履。怀德人。高丽末。有讳吉臣。及第位至闾门祗侯。于府君为六世祖。五世祖讳尚文。文科及第。高祖讳彬。直长。高祖妣阳城李氏。大司谏壅之女。侍中春富之孙。曾祖讳铁均。以文行被荐。司判义州。曾祖妣海平尹氏。直长济之女。南原府使处信之孙。参议朴积善之外孙。祖讳友参。正德丙子。生员。笃孝能文。祖妣坡平尹氏。御侮将军𡎈之女。春川府使师商之孙。高林正薰之外孙。考讳润琳。宣务郎。妣宜人清州韩氏。宣略将军瑚之女。上党府院君渥之后。进士安淑禧之外孙。以有明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十一月二十六日生
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51L 页
 府君。府君生而有不凡之质。在童子。日受学于生员公及舅进士公讳仁祖。日月将就。未十岁。晓文义。至十五六岁时。以善属文知名于乡解。二十岁前。遂成钜儒。不复从师问业。其后尝曰。人于二十岁前读书识门户。然后可以为儒矣。所中司马监试,文科初试不知其几。而命与仇谋。卒之泣刖。时人惜之。府君虽穷经缀文。贯穿场屋。而其立定脚跟处。实在吾儒行谊上矣。天性至孝。又深得事亲为大抵道理。顺事二亲。极尽诚敬。昏定晨省。出入告面。左右就养等礼。无不合于典礼者。初聘闵氏于牙山。自行见舅姑礼以后。即还于牙。别其家以居。盖居此则生理不足。且不欲以生理废业故也。然府君在彼常少。在此常多。或在山寺读书。未曾自理生业。府君常以无私财不能养亲为欠。至是乃得遂其素志。衣服酒食。各种海错。凡可以便身称口者。陆续以进。如是者几十五年。以至筑室于此。举家大归之后。亦益竭诚。府君忠养之道类此。宣务公病风痹。委顿床席者有年。而府君与吾先府君。侍侧不离。尽心调治。至有人所难及者。府君平日不喜歌。及亲癠。无以慰悦其怀。则常歌之不辍。岁庚辰。宣务公弃背。府君执丧。哀礼两尽。庐于墓傍。朝夕馈奠外晨昏哭冢。不以风两寒暑而阙之。丧
府君。府君生而有不凡之质。在童子。日受学于生员公及舅进士公讳仁祖。日月将就。未十岁。晓文义。至十五六岁时。以善属文知名于乡解。二十岁前。遂成钜儒。不复从师问业。其后尝曰。人于二十岁前读书识门户。然后可以为儒矣。所中司马监试,文科初试不知其几。而命与仇谋。卒之泣刖。时人惜之。府君虽穷经缀文。贯穿场屋。而其立定脚跟处。实在吾儒行谊上矣。天性至孝。又深得事亲为大抵道理。顺事二亲。极尽诚敬。昏定晨省。出入告面。左右就养等礼。无不合于典礼者。初聘闵氏于牙山。自行见舅姑礼以后。即还于牙。别其家以居。盖居此则生理不足。且不欲以生理废业故也。然府君在彼常少。在此常多。或在山寺读书。未曾自理生业。府君常以无私财不能养亲为欠。至是乃得遂其素志。衣服酒食。各种海错。凡可以便身称口者。陆续以进。如是者几十五年。以至筑室于此。举家大归之后。亦益竭诚。府君忠养之道类此。宣务公病风痹。委顿床席者有年。而府君与吾先府君。侍侧不离。尽心调治。至有人所难及者。府君平日不喜歌。及亲癠。无以慰悦其怀。则常歌之不辍。岁庚辰。宣务公弃背。府君执丧。哀礼两尽。庐于墓傍。朝夕馈奠外晨昏哭冢。不以风两寒暑而阙之。丧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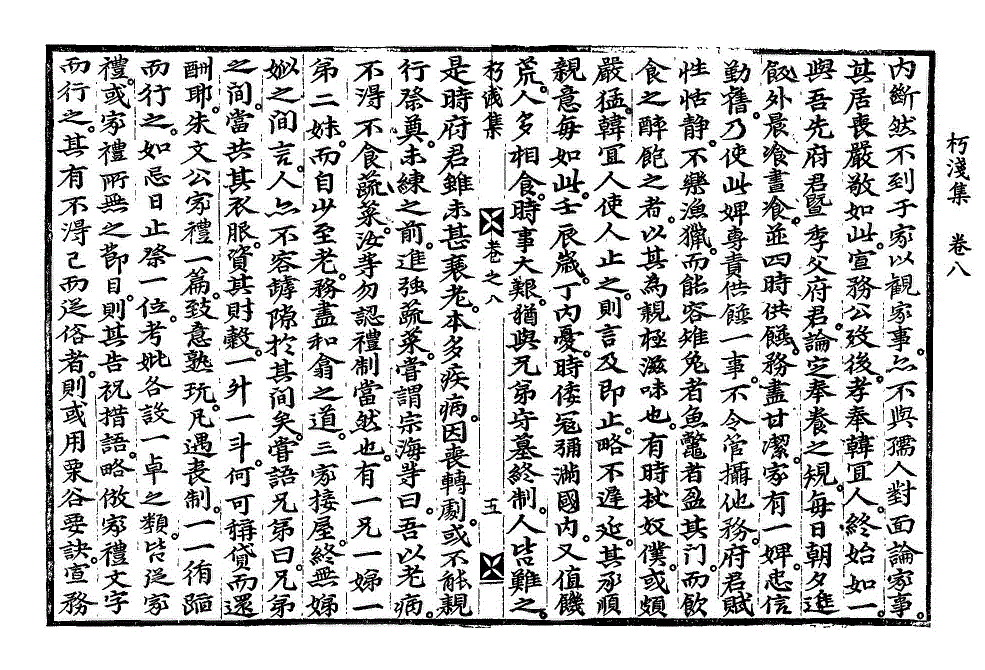 内断然不到于家以观家事。亦不与孺人对面论家事。其居丧严敬如此。宣务公殁后。孝奉韩宜人。终始如一。与吾先府君暨季父府君。论定奉养之规。每日朝夕进饭外晨餐昼餐。并四时供馔。务尽甘洁。家有一婢。忠信勤旧。乃使此婢专责供馔一事。不令管摄他务。府君赋性恬静。不乐渔猎。而能容雉兔者鱼鳖者盈其门。而饮食之醉饱之者。以其为亲极滋味也。有时杖奴仆。或颇严猛。韩宜人使人止之。则言及即止。略不迟延。其承顺亲意每如此。壬辰岁。丁内忧。时倭寇弥满国内。又值饥荒。人多相食。时事大艰。犹与兄弟守墓终制。人皆难之。是时府君虽未甚衰老。本多疾病。因丧转剧。或不能亲行祭奠。未练之前。进强蔬菜。尝谓宗海等曰。吾以老病。不得不食蔬菜。汝等勿认礼制当然也。有一兄一娣一弟二妹。而自少至老。务尽和翕之道。三家接屋。终无娣娰之间言。人亦不容罅隙于其间矣。尝语兄弟曰。兄弟之间。当共其衣服。资其财谷。一外一斗。何可称贷而还酬耶。朱文公家礼一篇。致意熟玩。凡遇丧制。一一循蹈而行之。如忌日止祭一位。考妣各设一卓之类。皆从家礼。或家礼所无之节目。则其告祝措语。略仿家礼文字而行之。其有不得已而从俗者。则或用栗谷要诀。宣务
内断然不到于家以观家事。亦不与孺人对面论家事。其居丧严敬如此。宣务公殁后。孝奉韩宜人。终始如一。与吾先府君暨季父府君。论定奉养之规。每日朝夕进饭外晨餐昼餐。并四时供馔。务尽甘洁。家有一婢。忠信勤旧。乃使此婢专责供馔一事。不令管摄他务。府君赋性恬静。不乐渔猎。而能容雉兔者鱼鳖者盈其门。而饮食之醉饱之者。以其为亲极滋味也。有时杖奴仆。或颇严猛。韩宜人使人止之。则言及即止。略不迟延。其承顺亲意每如此。壬辰岁。丁内忧。时倭寇弥满国内。又值饥荒。人多相食。时事大艰。犹与兄弟守墓终制。人皆难之。是时府君虽未甚衰老。本多疾病。因丧转剧。或不能亲行祭奠。未练之前。进强蔬菜。尝谓宗海等曰。吾以老病。不得不食蔬菜。汝等勿认礼制当然也。有一兄一娣一弟二妹。而自少至老。务尽和翕之道。三家接屋。终无娣娰之间言。人亦不容罅隙于其间矣。尝语兄弟曰。兄弟之间。当共其衣服。资其财谷。一外一斗。何可称贷而还酬耶。朱文公家礼一篇。致意熟玩。凡遇丧制。一一循蹈而行之。如忌日止祭一位。考妣各设一卓之类。皆从家礼。或家礼所无之节目。则其告祝措语。略仿家礼文字而行之。其有不得已而从俗者。则或用栗谷要诀。宣务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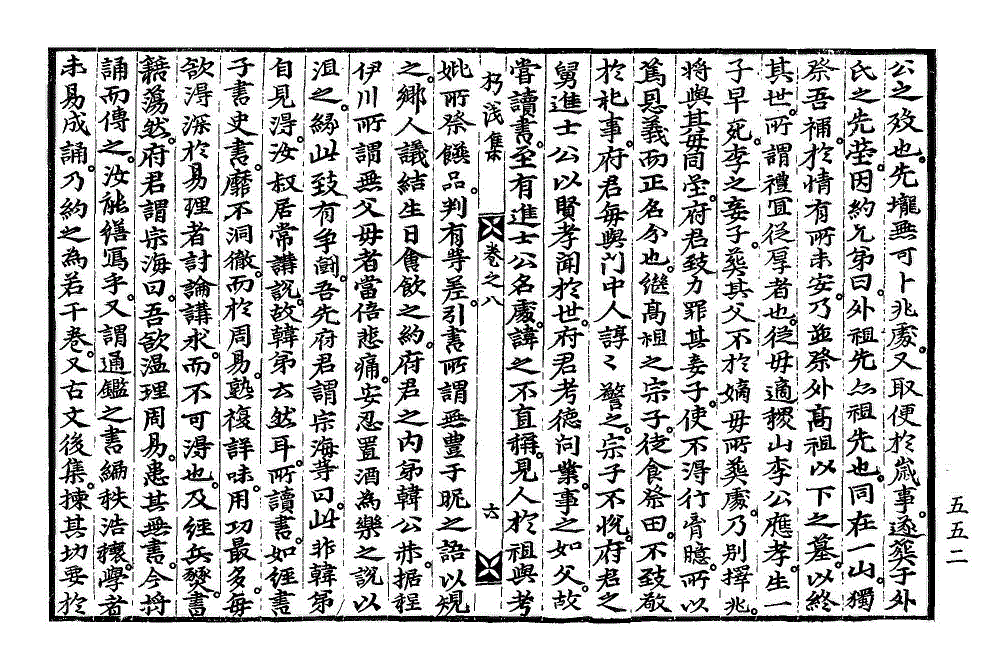 公之殁也。先垄无可卜兆处。又取便于岁事。遂葬于外氏之先茔。因约兄弟曰。外祖先亦祖先也。同在一山。独祭吾祢。于情有所未安。乃并祭外高祖以下之墓。以终其世。所谓礼宜从厚者也。从母适稷山李公应孝。生一子早死。李之妾子。葬其父不于嫡母所葬处。乃别择兆。将与其母同茔。府君致力罪其妾子。使不得行胸臆。所以笃恩义而正名分也。继高祖之宗子。徒食祭田。不致敬于祀事。府君每与门中人谆谆警之。宗子不悦。府君之舅进士公以贤孝闻于世。府君考德问业。事之如父。故尝读书。至有进士公名处。讳之不直称。见人于祖与考妣所祭馔品。判有等差。引书所谓无丰于昵之语以规之。乡人议结生日会饮之约。府君之内弟韩公赫。据程伊川所谓无父母者当倍悲痛。安忍置酒为乐之说以沮之。缘此致有争斗。吾先府君谓宗海等曰。此非韩弟自见得。汝叔居常讲说。故韩弟云然耳。所读书。如经书子书史书。靡不洞彻。而于周易。熟复详味。用功最多。每欲得深于易理者讨论讲求。而不可得也。及经兵燹。书籍荡然。府君谓宗海曰。吾欲温理周易。患其无书。今将诵而传之。汝能缮写乎。又谓通鉴之书编秩浩穰。学者未易成诵。乃约之为若干卷。又古文后集。拣其切要于
公之殁也。先垄无可卜兆处。又取便于岁事。遂葬于外氏之先茔。因约兄弟曰。外祖先亦祖先也。同在一山。独祭吾祢。于情有所未安。乃并祭外高祖以下之墓。以终其世。所谓礼宜从厚者也。从母适稷山李公应孝。生一子早死。李之妾子。葬其父不于嫡母所葬处。乃别择兆。将与其母同茔。府君致力罪其妾子。使不得行胸臆。所以笃恩义而正名分也。继高祖之宗子。徒食祭田。不致敬于祀事。府君每与门中人谆谆警之。宗子不悦。府君之舅进士公以贤孝闻于世。府君考德问业。事之如父。故尝读书。至有进士公名处。讳之不直称。见人于祖与考妣所祭馔品。判有等差。引书所谓无丰于昵之语以规之。乡人议结生日会饮之约。府君之内弟韩公赫。据程伊川所谓无父母者当倍悲痛。安忍置酒为乐之说以沮之。缘此致有争斗。吾先府君谓宗海等曰。此非韩弟自见得。汝叔居常讲说。故韩弟云然耳。所读书。如经书子书史书。靡不洞彻。而于周易。熟复详味。用功最多。每欲得深于易理者讨论讲求。而不可得也。及经兵燹。书籍荡然。府君谓宗海曰。吾欲温理周易。患其无书。今将诵而传之。汝能缮写乎。又谓通鉴之书编秩浩穰。学者未易成诵。乃约之为若干卷。又古文后集。拣其切要于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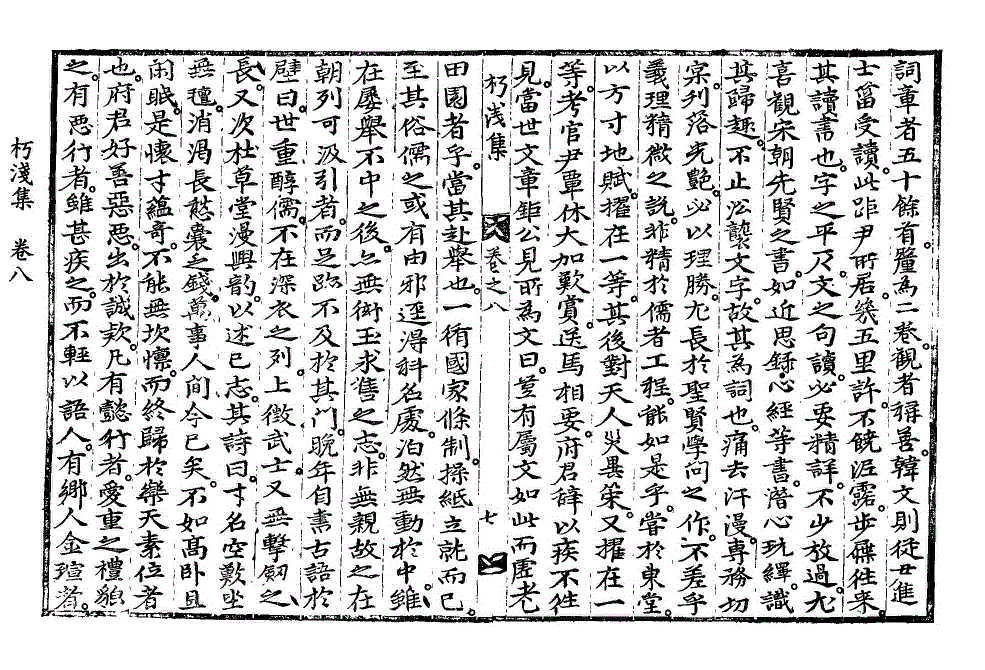 词章者五十馀首。釐为二卷。观者称善。韩文则从丑进士菑受读。此距尹所居。几五里许。不饶泥露。步屧往来。其读书也。字之平仄。文之句读。必要精详。不少放过。尤喜观宋朝先贤之书。如近思录,心经等书。潜心玩绎。识其归趣。不止沿袭文字。故其为词也。痛去汗漫。专务切实。刋落光艳。必以理胜。尤长于圣贤学问之作。不差乎义理精微之说。非精于儒者工程。能如是乎。尝于东堂。以方寸地赋。擢在一等。其后对天人灾异荣。又擢在一等。考官尹覃休大加叹赏。送马相要。府君辞以疾不往见。当世文章钜公见所为文曰。岂有属文如此而虚老田园者乎。当其赴举也。一循国家条制。操纸立就而已。至其俗儒之或有由邪径得科名处。泊然无动于中。虽在屡举不中之后。亦无衒玉求售之志。非无亲故之在朝列可汲引者。而足迹不及于其门。晚年自书古语于壁曰。世重醇儒。不在深衣之列。上徵武士。又无击剑之长。又次杜草堂漫兴韵。以述己志。其诗曰。寸名空叹坐无毡。消渴长愁囊之钱。万事人间今已矣。不如高卧且闲眠。是怀寸蕴奇。不能无坎懔。而终归于乐天素位者也。府君好善恶恶。出于诚款。凡有懿行者。爱重之礼貌之。有恶行者。虽甚疾之。而不轻以语人。有乡人金瑄者。
词章者五十馀首。釐为二卷。观者称善。韩文则从丑进士菑受读。此距尹所居。几五里许。不饶泥露。步屧往来。其读书也。字之平仄。文之句读。必要精详。不少放过。尤喜观宋朝先贤之书。如近思录,心经等书。潜心玩绎。识其归趣。不止沿袭文字。故其为词也。痛去汗漫。专务切实。刋落光艳。必以理胜。尤长于圣贤学问之作。不差乎义理精微之说。非精于儒者工程。能如是乎。尝于东堂。以方寸地赋。擢在一等。其后对天人灾异荣。又擢在一等。考官尹覃休大加叹赏。送马相要。府君辞以疾不往见。当世文章钜公见所为文曰。岂有属文如此而虚老田园者乎。当其赴举也。一循国家条制。操纸立就而已。至其俗儒之或有由邪径得科名处。泊然无动于中。虽在屡举不中之后。亦无衒玉求售之志。非无亲故之在朝列可汲引者。而足迹不及于其门。晚年自书古语于壁曰。世重醇儒。不在深衣之列。上徵武士。又无击剑之长。又次杜草堂漫兴韵。以述己志。其诗曰。寸名空叹坐无毡。消渴长愁囊之钱。万事人间今已矣。不如高卧且闲眠。是怀寸蕴奇。不能无坎懔。而终归于乐天素位者也。府君好善恶恶。出于诚款。凡有懿行者。爱重之礼貌之。有恶行者。虽甚疾之。而不轻以语人。有乡人金瑄者。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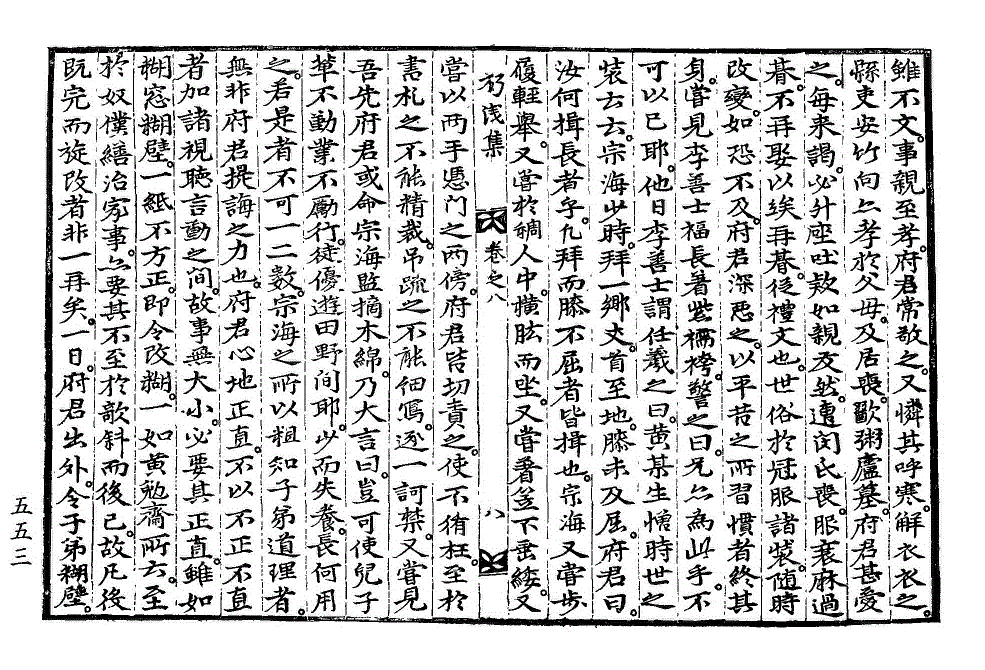 虽不文。事亲至孝。府君常敬之。又怜其呼寒。解衣衣之。县吏安竹向亦孝于父母。及居丧。歠粥庐墓。府君甚爱之。每来谒。必升座吐款如亲友然。遭闵氏丧。服衰麻过期。不再娶以俟再期。从礼文也。世俗于冠服诸装。随时改变。如恐不及。府君深恶之。以平昔之所习惯者终其身。尝见李善士福长着紫襦裤。警之日。兄亦为此乎。不可以已耶。他日李善士谓任羲之曰。黄某生憎时世之装云云。宗海少时。拜一乡丈。首至地。膝未及屈。府君曰。汝何揖长者乎。凡拜而膝不屈者皆揖也。宗海又尝步履轻举。又尝于稠人中。横肱而坐。又尝着笠下垂緌。又尝以两手凭门之两傍。府君皆切责之。使不循枉。至于书札之不能精裁。吊疏之不能细写。逐一诃禁。又尝见吾先府君或命宗海监摘木绵。乃大言曰。岂可使儿子辈不勤业不励行。徒优游田野间耶。少而失养。长何用之。若是者不可一二数。宗海之所以粗知子弟道理者。无非府君提诲之力也。府君心地正直。不以不正不直者加诸视听言动之间。故事无大小。必要其正直。虽如糊窗糊壁。一纸不方正。即令改糊。一如黄勉斋所云。至于奴仆缮治家事。亦要其不至于欹斜而后已。故凡役既完而旋改者非一再矣。一日。府君出外。令子弟糊壁。
虽不文。事亲至孝。府君常敬之。又怜其呼寒。解衣衣之。县吏安竹向亦孝于父母。及居丧。歠粥庐墓。府君甚爱之。每来谒。必升座吐款如亲友然。遭闵氏丧。服衰麻过期。不再娶以俟再期。从礼文也。世俗于冠服诸装。随时改变。如恐不及。府君深恶之。以平昔之所习惯者终其身。尝见李善士福长着紫襦裤。警之日。兄亦为此乎。不可以已耶。他日李善士谓任羲之曰。黄某生憎时世之装云云。宗海少时。拜一乡丈。首至地。膝未及屈。府君曰。汝何揖长者乎。凡拜而膝不屈者皆揖也。宗海又尝步履轻举。又尝于稠人中。横肱而坐。又尝着笠下垂緌。又尝以两手凭门之两傍。府君皆切责之。使不循枉。至于书札之不能精裁。吊疏之不能细写。逐一诃禁。又尝见吾先府君或命宗海监摘木绵。乃大言曰。岂可使儿子辈不勤业不励行。徒优游田野间耶。少而失养。长何用之。若是者不可一二数。宗海之所以粗知子弟道理者。无非府君提诲之力也。府君心地正直。不以不正不直者加诸视听言动之间。故事无大小。必要其正直。虽如糊窗糊壁。一纸不方正。即令改糊。一如黄勉斋所云。至于奴仆缮治家事。亦要其不至于欹斜而后已。故凡役既完而旋改者非一再矣。一日。府君出外。令子弟糊壁。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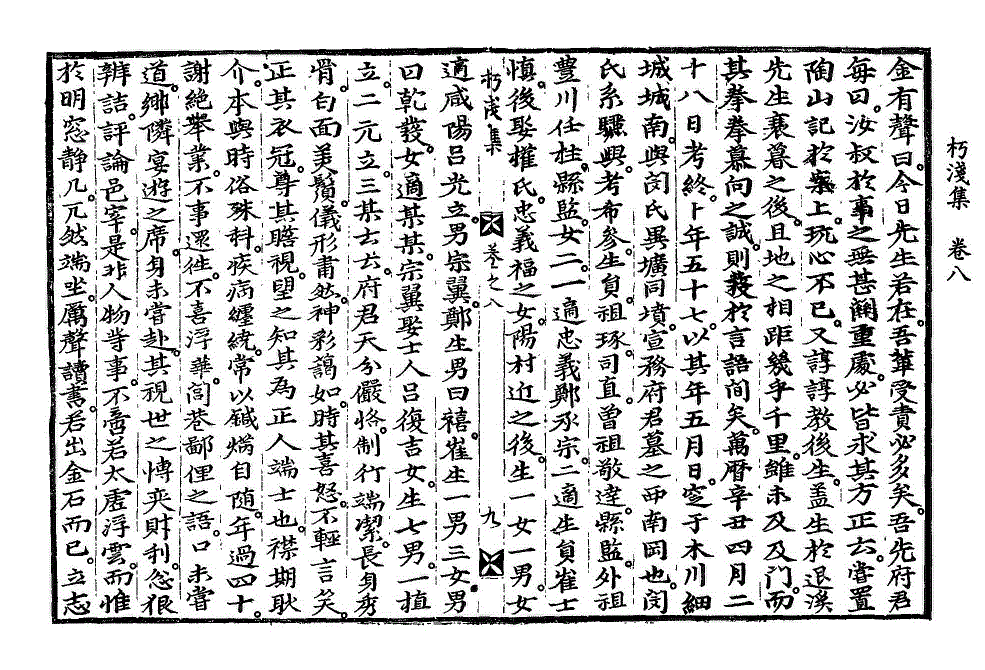 金有声曰。今日先生若在。吾辈受责必多矣。吾先府君每曰。汝叔于事之无甚关重处。必皆求其方正云。尝置陶山记于案上。玩心不已。又谆谆教后生。盖生于退溪先生衰暮之后。且地之相距几乎千里。虽未及及门。而其拳拳慕向之诚。则发于言语间矣。万历辛丑四月二十八日考终。卜年五十七。以其年五月日。窆于木川细城城南。与闵氏异圹同坟。宣务府君墓之西南冈也。闵氏系骊兴。考希参。生员。祖琢。司直。曾祖敬达。县监。外祖丰川任柱。县监。女二。一适忠义郑承宗。二适生员崔士慎。后娶权氏。忠义福之女。阳村近之后。生一女一男。女适咸阳吕光立。男宗翼。郑生男曰禧。崔生一男三女。男曰乾发。女适某某。宗翼娶士人吕复吉女。生七男。一植立。二元立。三某云云。府君天分俨恪。制行端洁。长身秀骨。白面美须。仪形肃然。神彩蔼如。时其喜怒。不轻言笑。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望之知其为正人端士也。襟期耿介。本与时俗殊科。疾病缠绕。常以针焫自随。年过四十。谢绝举业。不事还往。不喜浮华。闾巷鄙俚之语。口未尝道。乡邻宴游之席。身未尝赴。其视世之博奕财利。忿狠辨诘。评论邑宰。是非人物等事。不啻若太虚浮云。而惟于明窗静几。兀然端坐。厉声读书。若出金石而已。立志
金有声曰。今日先生若在。吾辈受责必多矣。吾先府君每曰。汝叔于事之无甚关重处。必皆求其方正云。尝置陶山记于案上。玩心不已。又谆谆教后生。盖生于退溪先生衰暮之后。且地之相距几乎千里。虽未及及门。而其拳拳慕向之诚。则发于言语间矣。万历辛丑四月二十八日考终。卜年五十七。以其年五月日。窆于木川细城城南。与闵氏异圹同坟。宣务府君墓之西南冈也。闵氏系骊兴。考希参。生员。祖琢。司直。曾祖敬达。县监。外祖丰川任柱。县监。女二。一适忠义郑承宗。二适生员崔士慎。后娶权氏。忠义福之女。阳村近之后。生一女一男。女适咸阳吕光立。男宗翼。郑生男曰禧。崔生一男三女。男曰乾发。女适某某。宗翼娶士人吕复吉女。生七男。一植立。二元立。三某云云。府君天分俨恪。制行端洁。长身秀骨。白面美须。仪形肃然。神彩蔼如。时其喜怒。不轻言笑。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望之知其为正人端士也。襟期耿介。本与时俗殊科。疾病缠绕。常以针焫自随。年过四十。谢绝举业。不事还往。不喜浮华。闾巷鄙俚之语。口未尝道。乡邻宴游之席。身未尝赴。其视世之博奕财利。忿狠辨诘。评论邑宰。是非人物等事。不啻若太虚浮云。而惟于明窗静几。兀然端坐。厉声读书。若出金石而已。立志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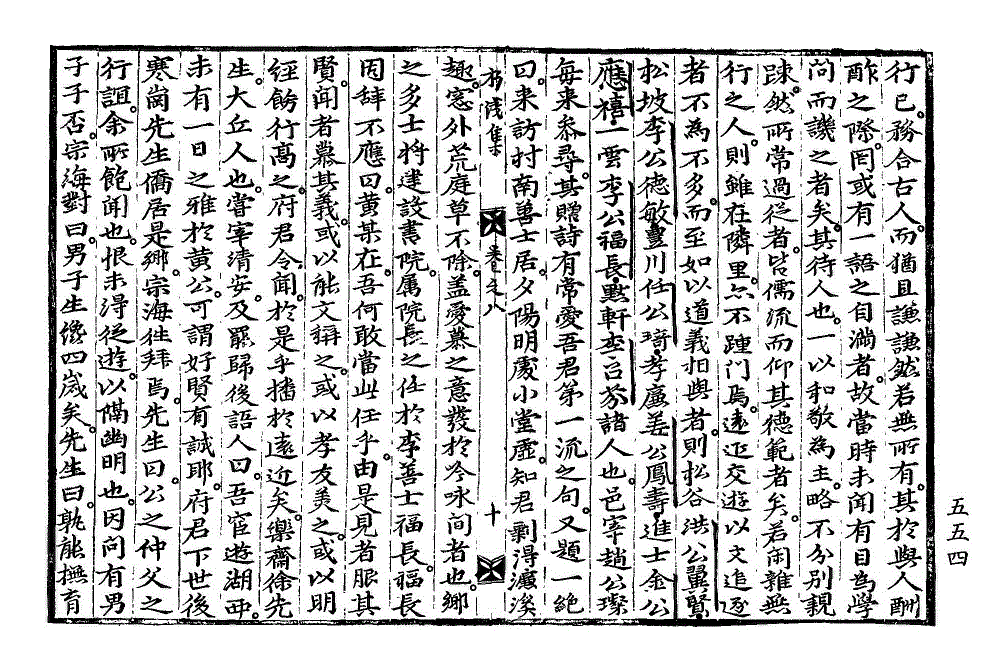 行已。务合古人。而犹且谦谦然若无所有。其于与人酬酢之际。罔或有一语之自满者。故当时未闻有目为学问而讥之者矣。其待人也。一以和敬为主。略不分别亲疏。然所常过从者。皆儒流而仰其德范者矣。若闲杂无行之人。则虽在邻里。亦不踵门焉。远近交游以文追逐者不为不多。而至如以道义相与者。则松谷洪公翼贤,松坡李公德敏,丰川任公琦,孝廉姜公凤寿,进士金公应禧,一云李公福长,默轩李召芬诸人也。邑宰赵公璨每来参寻。其赠诗有常爱吾君弟一流之句。又题一绝曰。来访村南善士居。夕阳明处小堂虚。知君剩得濂溪趣。窗外荒庭草不除。盖爱慕之意发于吟咏间者也。乡之多士将建设书院。属院长之任于李善士福长。福长固辞不应曰。黄某在。吾何敢当此任乎。由是见者服其贤。闻者慕其义。或以能文称之。或以孝友美之。或以明经饬行高之。府君令闻。于是乎播于远近矣。乐斋徐先生。大丘人也。尝宰清安。及罢归后语人曰。吾宦游湖西。未有一日之雅于黄公。可谓好贤有诚耶。府君下世后寒冈先生侨居是乡。宗海往拜焉。先生曰。公之仲父之行谊。余所饱闻也。恨未得从游。以隔幽明也。因问有男子子否。宗海对曰。男子生才四岁矣。先生曰。孰能抚育
行已。务合古人。而犹且谦谦然若无所有。其于与人酬酢之际。罔或有一语之自满者。故当时未闻有目为学问而讥之者矣。其待人也。一以和敬为主。略不分别亲疏。然所常过从者。皆儒流而仰其德范者矣。若闲杂无行之人。则虽在邻里。亦不踵门焉。远近交游以文追逐者不为不多。而至如以道义相与者。则松谷洪公翼贤,松坡李公德敏,丰川任公琦,孝廉姜公凤寿,进士金公应禧,一云李公福长,默轩李召芬诸人也。邑宰赵公璨每来参寻。其赠诗有常爱吾君弟一流之句。又题一绝曰。来访村南善士居。夕阳明处小堂虚。知君剩得濂溪趣。窗外荒庭草不除。盖爱慕之意发于吟咏间者也。乡之多士将建设书院。属院长之任于李善士福长。福长固辞不应曰。黄某在。吾何敢当此任乎。由是见者服其贤。闻者慕其义。或以能文称之。或以孝友美之。或以明经饬行高之。府君令闻。于是乎播于远近矣。乐斋徐先生。大丘人也。尝宰清安。及罢归后语人曰。吾宦游湖西。未有一日之雅于黄公。可谓好贤有诚耶。府君下世后寒冈先生侨居是乡。宗海往拜焉。先生曰。公之仲父之行谊。余所饱闻也。恨未得从游。以隔幽明也。因问有男子子否。宗海对曰。男子生才四岁矣。先生曰。孰能抚育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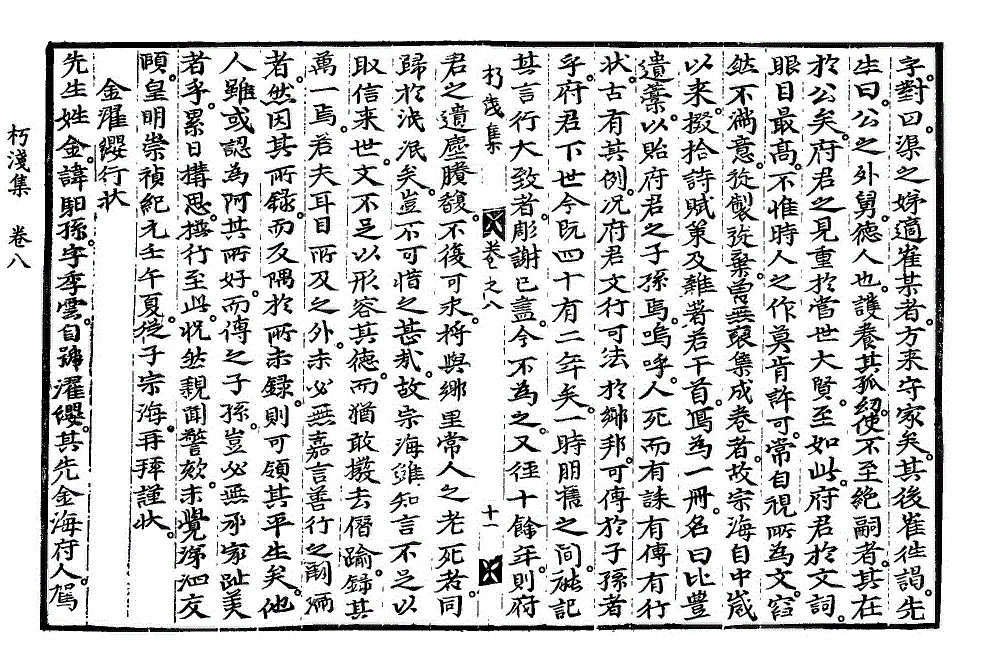 乎。对曰。渠之娣适崔某者。方来守家矣。其后崔往谒。先生曰。公之外舅。德人也。护养其孤幼。使不至绝嗣者。其在于公矣。府君之见重于当世大贤。至如此。府君于文词。眼目最高。不惟时人之作莫肯许可。常自视所为文。窞然不满意。旋制旋弃。曾无裒集成卷者。故宗海自中岁以来。掇拾诗赋策及杂著若干首。写为一册。名曰比丰遗藁。以贻府君之子孙焉。呜呼。人死而有诔有传有行状。古有其例。况府君文行可法于乡邦。可传于子孙者乎。府君下世今既四十有二年矣。一时朋旧之间。能记其言行大致者。彫谢已尽。今不为之。又径十馀年。则府君之遗尘剩馥。不复可求。将与乡里常人之老死者。同归于泯泯矣。岂不可惜之甚哉。故宗海虽知言不足以取信来世。文不足以形容其德。而犹敢拨去僭踰。录其万一焉。若夫耳目所及之外。未必无嘉言善行之阙满者。然因其所录。而反隅于所未录。则可领其平生矣。他人虽或认为阿其所好。而传之子孙。岂必无承家趾美者乎。累日搆思。撰行至此。恍然亲闻警欬。未觉涕泗交颐。皇明崇祯纪元壬午夏。从子宗海。再拜谨状。
乎。对曰。渠之娣适崔某者。方来守家矣。其后崔往谒。先生曰。公之外舅。德人也。护养其孤幼。使不至绝嗣者。其在于公矣。府君之见重于当世大贤。至如此。府君于文词。眼目最高。不惟时人之作莫肯许可。常自视所为文。窞然不满意。旋制旋弃。曾无裒集成卷者。故宗海自中岁以来。掇拾诗赋策及杂著若干首。写为一册。名曰比丰遗藁。以贻府君之子孙焉。呜呼。人死而有诔有传有行状。古有其例。况府君文行可法于乡邦。可传于子孙者乎。府君下世今既四十有二年矣。一时朋旧之间。能记其言行大致者。彫谢已尽。今不为之。又径十馀年。则府君之遗尘剩馥。不复可求。将与乡里常人之老死者。同归于泯泯矣。岂不可惜之甚哉。故宗海虽知言不足以取信来世。文不足以形容其德。而犹敢拨去僭踰。录其万一焉。若夫耳目所及之外。未必无嘉言善行之阙满者。然因其所录。而反隅于所未录。则可领其平生矣。他人虽或认为阿其所好。而传之子孙。岂必无承家趾美者乎。累日搆思。撰行至此。恍然亲闻警欬。未觉涕泗交颐。皇明崇祯纪元壬午夏。从子宗海。再拜谨状。金濯缨行状
先生姓金。讳驲孙。字季云。自号濯缨。其先金海府人。驾
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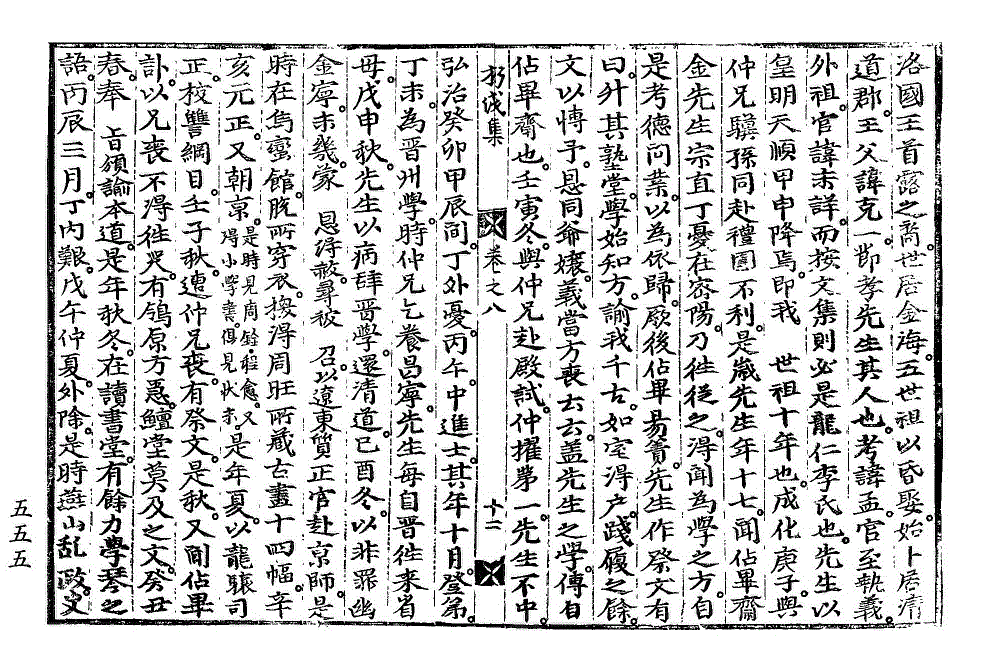 洛国王首露之裔。世居金海。五世祖以昏娶。始卜居清道郡。王父讳克一。节孝先生其人也。考讳孟。官至执义。外祖。官讳未详。而按文集则必是龙仁李氏也。先生以皇明天顺甲申降焉。即我 世祖十年也。成化庚子。与仲兄骥孙同赴礼围不利。是岁先生年十七。闻佔毕斋金先生宗直丁忧在密阳。乃往从之。得闻为学之方。自是考德问业。以为依归。厥后佔毕易箦。先生作祭文有曰。升其塾堂。学始知方。谕我千古。如室得户。践履之馀。文以博予。恩同爷娘。义当方丧云云。盖先生之学。传自佔毕斋也。壬寅冬。与仲兄赴殿试。仲擢第一。先生不中。弘治癸卯甲辰间。丁外忧。丙午。中进士。其年十月。登第。丁未。为晋州学。时仲兄乞养昌宁。先生每自晋往来省母。戊申秋。先生以病辞晋学。还清道。己酉冬。以非罪幽金宁。未几。蒙 恩得赦。寻被 召。以辽东质正官赴京师。是时在乌蛮馆。脱所穿衣。换得周旺所藏古画十四幅。辛亥元正。又朝京。(是时见周铨,程愈。又得小学书。俱见状末。)是年夏。以龙骧司正。校雠纲目。壬子秋。遭仲兄丧。有祭文。是秋。又闻佔毕讣。以兄丧不得往哭。有鸰原方急。鳣堂莫及之文。癸丑春。奉 旨须谕本道。是年秋冬。在读书堂。有馀力学琴之语。丙辰三月。丁内艰。戊午仲夏。外除。是时燕山乱政。史
洛国王首露之裔。世居金海。五世祖以昏娶。始卜居清道郡。王父讳克一。节孝先生其人也。考讳孟。官至执义。外祖。官讳未详。而按文集则必是龙仁李氏也。先生以皇明天顺甲申降焉。即我 世祖十年也。成化庚子。与仲兄骥孙同赴礼围不利。是岁先生年十七。闻佔毕斋金先生宗直丁忧在密阳。乃往从之。得闻为学之方。自是考德问业。以为依归。厥后佔毕易箦。先生作祭文有曰。升其塾堂。学始知方。谕我千古。如室得户。践履之馀。文以博予。恩同爷娘。义当方丧云云。盖先生之学。传自佔毕斋也。壬寅冬。与仲兄赴殿试。仲擢第一。先生不中。弘治癸卯甲辰间。丁外忧。丙午。中进士。其年十月。登第。丁未。为晋州学。时仲兄乞养昌宁。先生每自晋往来省母。戊申秋。先生以病辞晋学。还清道。己酉冬。以非罪幽金宁。未几。蒙 恩得赦。寻被 召。以辽东质正官赴京师。是时在乌蛮馆。脱所穿衣。换得周旺所藏古画十四幅。辛亥元正。又朝京。(是时见周铨,程愈。又得小学书。俱见状末。)是年夏。以龙骧司正。校雠纲目。壬子秋。遭仲兄丧。有祭文。是秋。又闻佔毕讣。以兄丧不得往哭。有鸰原方急。鳣堂莫及之文。癸丑春。奉 旨须谕本道。是年秋冬。在读书堂。有馀力学琴之语。丙辰三月。丁内艰。戊午仲夏。外除。是时燕山乱政。史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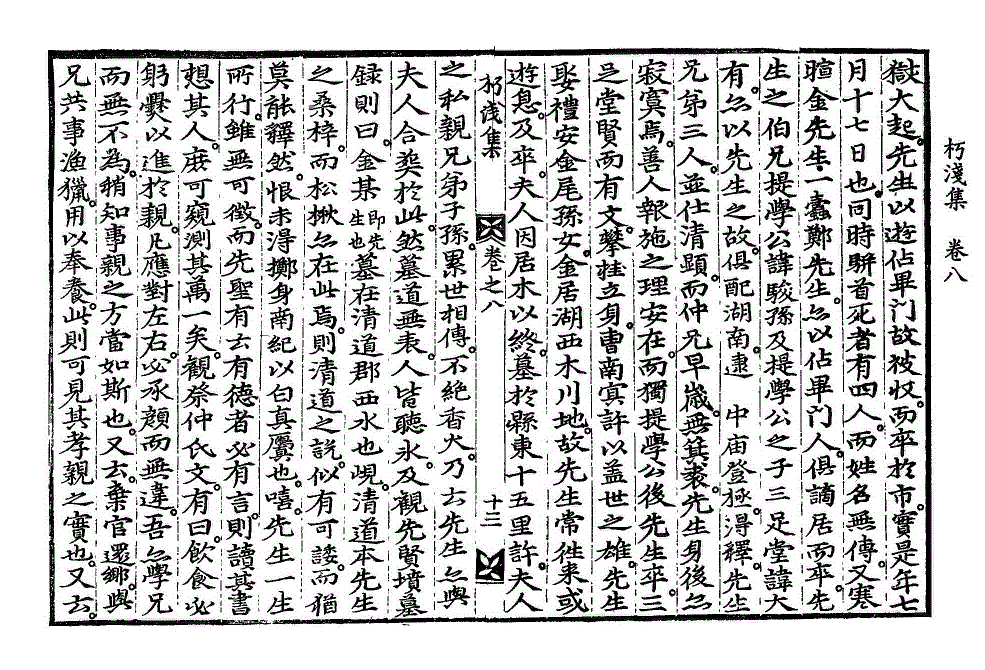 狱大起。先生以游佔毕门故被收。而卒于市。实是年七月十七日也。同时骈首死者有四人。而姓名无传。又寒暄金先生,一蠹郑先生。亦以佔毕门人。俱谪居而卒。先生之伯兄提学公讳骏孙及提学公之子三足堂讳大有。亦以先生之故。俱配湖南。逮 中庙登极。得释。先生兄弟三人。并仕清显。而仲兄早岁。无箕裘。先生身后亦寂寞焉。善人报施之理安在。而独提学公后先生卒。三足堂贤而有文。攀桂立身。曹南冥许以盖世之雄。先生娶礼安金尾孙女。金居湖西木川地。故先生常往来或游息。及卒。夫人因居木以终。墓于县东十五里许。夫人之私亲兄弟子孙。累世相传。不绝香火。乃云先生亦与夫人合葬于此。然墓道无表。人皆听冰。及观先贤坟墓录则曰。金某(即先生也)墓在清道郡西水也岘。清道本先生之桑梓。而松楸亦在此焉。则清道之说。似有可诿。而犹莫能释然。恨未得掷身南纪以白真赝也。嘻。先生一生所行。虽无可徵。而先圣有云有德者必有言。则读其书想其人。庶可窥测其万一矣。观祭仲氏文。有曰。饮食必躬爨以进于亲。凡应对左右。必承颜而无违。吾亦学兄而无不为。稍知事亲之方当如斯也。又云。弃官还乡。与兄共事渔猎。用以奉养。此则可见其孝亲之实也。又云。
狱大起。先生以游佔毕门故被收。而卒于市。实是年七月十七日也。同时骈首死者有四人。而姓名无传。又寒暄金先生,一蠹郑先生。亦以佔毕门人。俱谪居而卒。先生之伯兄提学公讳骏孙及提学公之子三足堂讳大有。亦以先生之故。俱配湖南。逮 中庙登极。得释。先生兄弟三人。并仕清显。而仲兄早岁。无箕裘。先生身后亦寂寞焉。善人报施之理安在。而独提学公后先生卒。三足堂贤而有文。攀桂立身。曹南冥许以盖世之雄。先生娶礼安金尾孙女。金居湖西木川地。故先生常往来或游息。及卒。夫人因居木以终。墓于县东十五里许。夫人之私亲兄弟子孙。累世相传。不绝香火。乃云先生亦与夫人合葬于此。然墓道无表。人皆听冰。及观先贤坟墓录则曰。金某(即先生也)墓在清道郡西水也岘。清道本先生之桑梓。而松楸亦在此焉。则清道之说。似有可诿。而犹莫能释然。恨未得掷身南纪以白真赝也。嘻。先生一生所行。虽无可徵。而先圣有云有德者必有言。则读其书想其人。庶可窥测其万一矣。观祭仲氏文。有曰。饮食必躬爨以进于亲。凡应对左右。必承颜而无违。吾亦学兄而无不为。稍知事亲之方当如斯也。又云。弃官还乡。与兄共事渔猎。用以奉养。此则可见其孝亲之实也。又云。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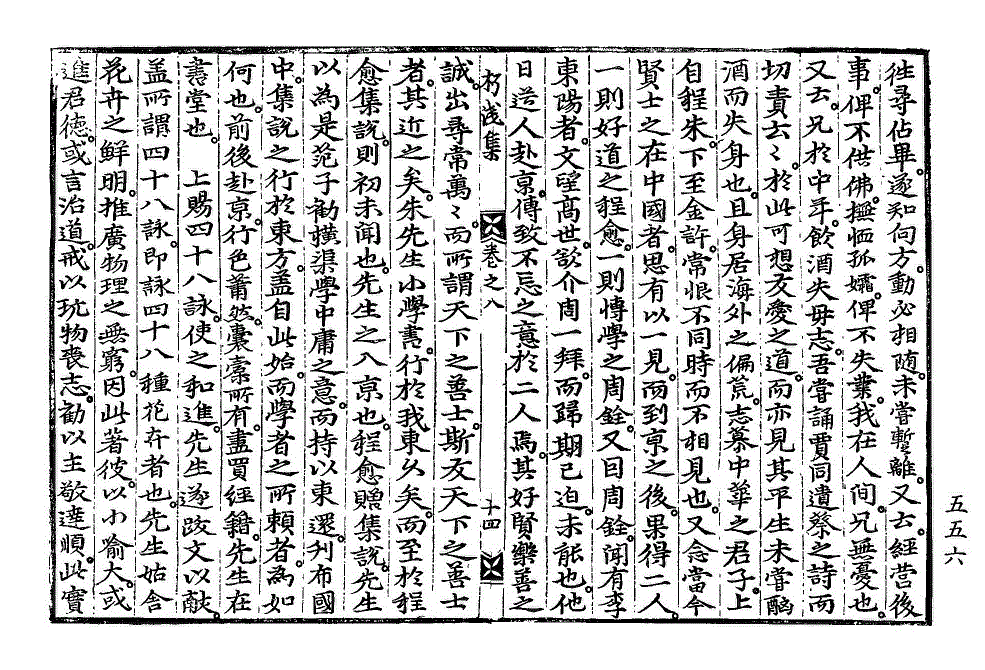 往寻佔毕。遂知向方。动必相随。未尝暂离。又云。经营后事。俾不供佛。抚恤孤孀。俾不失业。我在人间。兄无忧也。又云。兄于中年。饮酒失母志。吾尝诵贾同遗蔡之诗而切责云云。于此可想友爱之道。而亦见其平生未尝酗酒而失身也。且身居海外之偏荒。志慕中华之君子。上自程朱。下至金许。常恨不同时而不相见也。又念当今贤士之在中国者。思有以一见。而到京之后。果得二人。一则好道之程愈。一则博学之周铨。又因周铨。闻有李东阳者。文望高世。欲介周一拜。而归期已迫。未能也。他日送人赴京。传致不忘之意于二人焉。其好贤乐善之诚。出寻常万万。而所谓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者。其近之矣。朱先生小学书。行于我东久矣。而至于程愈集说。则初未闻也。先生之入京也。程愈赠集说。先生以为是范子劝横渠学中庸之意。而持以东还。刊布国中。集说之行于东方。盖自此始。而学者之所赖者。为如何也。前后赴京。行色萧然。囊橐所有。尽买经籍。先生在书堂也。 上赐四十八咏。使之和进。先生遂跋文以献。盖所谓四十八咏。即咏四十八种花卉者也。先生姑舍花卉之鲜明。推广物理之无穷。因此著彼。以小喻大。或进君德。或言治道。戒以玩物丧志。劝以主敬达顺。此实
往寻佔毕。遂知向方。动必相随。未尝暂离。又云。经营后事。俾不供佛。抚恤孤孀。俾不失业。我在人间。兄无忧也。又云。兄于中年。饮酒失母志。吾尝诵贾同遗蔡之诗而切责云云。于此可想友爱之道。而亦见其平生未尝酗酒而失身也。且身居海外之偏荒。志慕中华之君子。上自程朱。下至金许。常恨不同时而不相见也。又念当今贤士之在中国者。思有以一见。而到京之后。果得二人。一则好道之程愈。一则博学之周铨。又因周铨。闻有李东阳者。文望高世。欲介周一拜。而归期已迫。未能也。他日送人赴京。传致不忘之意于二人焉。其好贤乐善之诚。出寻常万万。而所谓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者。其近之矣。朱先生小学书。行于我东久矣。而至于程愈集说。则初未闻也。先生之入京也。程愈赠集说。先生以为是范子劝横渠学中庸之意。而持以东还。刊布国中。集说之行于东方。盖自此始。而学者之所赖者。为如何也。前后赴京。行色萧然。囊橐所有。尽买经籍。先生在书堂也。 上赐四十八咏。使之和进。先生遂跋文以献。盖所谓四十八咏。即咏四十八种花卉者也。先生姑舍花卉之鲜明。推广物理之无穷。因此著彼。以小喻大。或进君德。或言治道。戒以玩物丧志。劝以主敬达顺。此实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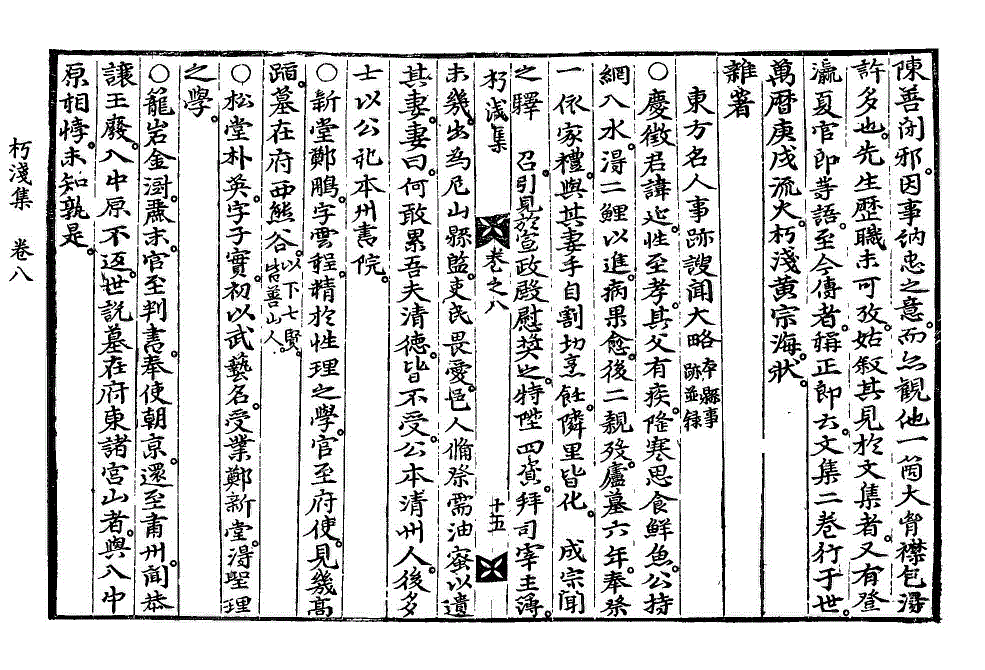 陈善闭邪。因事纳忠之意。而亦观他一个大胸襟包得许多也。先生历职未可考。姑叙其见于文集者。又有登瀛夏官郎等语。至今传者。称正郎云。文集二卷行于世。万历庚戌流火。朽浅黄宗海。状。
陈善闭邪。因事纳忠之意。而亦观他一个大胸襟包得许多也。先生历职未可考。姑叙其见于文集者。又有登瀛夏官郎等语。至今传者。称正郎云。文集二卷行于世。万历庚戌流火。朽浅黄宗海。状。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杂著
东方名人事迹謏闻大略(本县事迹并录)
○庆徵君讳延。性至孝。其父有疾。隆寒思食鲜鱼。公持网入水。汤二鲤以进。病果愈。后二亲殁。庐墓六年。奉祭一依家礼。与其妻手自割切烹饪。邻里皆化。 成宗闻之驿 召引见于宣政殿慰奖之。特升四资。拜司宰主簿。未几。出为尼山县监。吏民畏爱。邑人备祭需油蜜以遗其妻。妻曰。何敢累吾夫清德。皆不受。公本清州人。后多士以公祀本州书院。
○新堂郑鹏。字云程。精于性理之学。官至府使。见几高蹈。墓在府西熊谷。(以下七贤。皆善山人。)
○松堂朴英。字子实。初以武艺名。受业郑新堂。得圣理之学。
○笼岩金澍。丽末。官至判书。奉使朝京。还至肃州。闻恭让王废。入中原不返。世说墓在府东诸宫山者。与入中原相悖。未知孰是。
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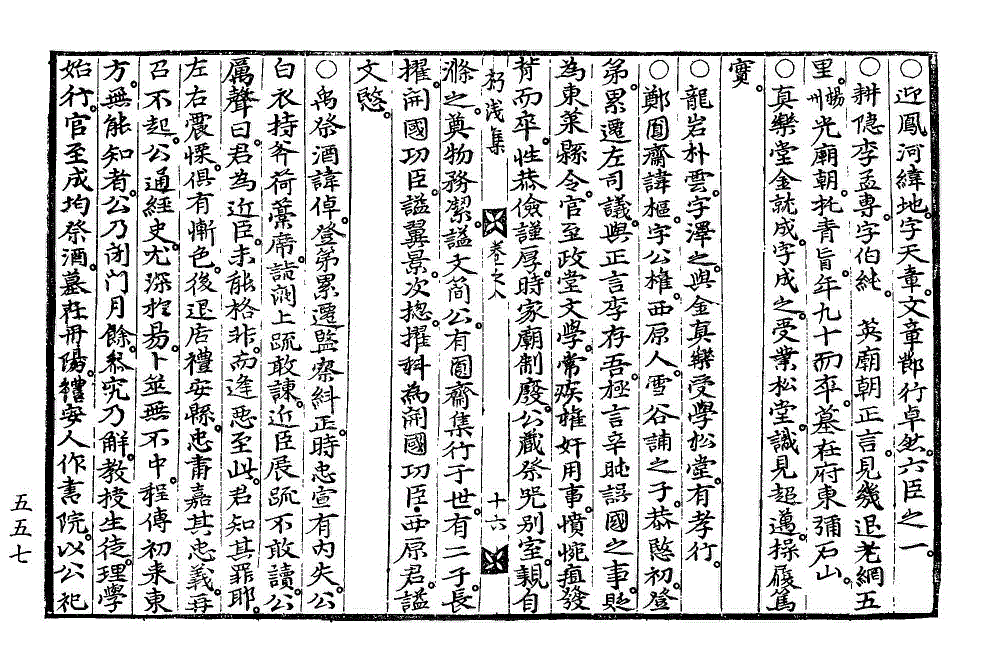 ○迎凤河纬地。字天章。文章节行卓然。六臣之一。
○迎凤河纬地。字天章。文章节行卓然。六臣之一。○耕隐李孟专。字伯纯。 英庙朝正言。见几退老网五里。(杨州)光庙朝。托青盲。年九十而卒。墓在府东弥石山。
○真乐堂金就成。字成之。受业松堂。识见起迈。操履笃实。
○龙岩朴云。字泽之。与金真乐受学松堂。有孝行。
○郑圆斋讳枢。字公权。西原人。雪谷誧之子。恭悯初。登第。累迁左司议。与正言李存吾。极言辛旽误国之事。贬为东莱县令。官至政堂文学。常疾权奸用事。愤惋疽发背而卒。性恭俭谨厚。时家庙制废。公藏祭器别室。亲自涤之。奠物务洁。谥文简公有圆斋集行于世。有二子。长擢。开国功臣。谥翼景。次总。擢科为开国功臣,西原君。谥文悯。
○禹祭酒讳倬。登第累迁监察纠正。时忠宣有内失。公白衣持斧荷藁席。诣阙上疏敢谏。近臣展疏不敢读。公厉声曰。君为近臣。未能格非。而逢恶至此。君知其罪耶。左右震慄。俱有惭色。后退居礼安县。忠肃嘉其忠义。再召不起。公通经史。尤深于易。卜筮无不中。程传初来东方。无能知者。公乃闭门月馀。参究乃解。教授生徒。理学始行。官至成均祭酒。墓在丹阳。礼安人作书院。以公祀
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58H 页
 之。名曰易东书院。今世禹姓者。多公之裔也。
之。名曰易东书院。今世禹姓者。多公之裔也。○新罗时百济来侵。丕宁突阵而死。子举真欲赴。奴合节曰。大人令合节奉阿郎还。以慰夫人。今子负父命。弃母慈可乎。执辔不放。举真曰。见父死而苟存。岂孝乎。以剑击合节臂。战死。合节曰。所天崩矣。不死何为。亦交锋而死。
○崔莹劝辛祦攻辽。 康献大王举义回军。复立王氏。赵浚,郑道传,南訚等欲推戴 康献大王。侍郎郑梦周。以道传,浚,訚等同心辅翼。令台谏劾流。将杀之。义安大君和,兴安君李济等。使麾下士赵英圭等。要于路击杀梦周。 康献大王大怒。因病笃。至不能言。 恭定大王即位。以专心所事。不贰其操。 赠谥文忠。旌门。
○洪武己巳冬。注书吉再弃官归家。 恭靖大王授奉常博士。再上书辞曰。云云。 恭靖问于权近曰。再抗节不仕。未审古人何以处之。对曰。严光不屈。光武从之。再若求去。不如使之自尽其心。 恭靖许归。复其家。 庄宪大王官其子。赠左司谏。旌门。
○金德崇。镇川人。尝弃官归养。至诚无怠。年六十二。遭母丧。庐墓三年。每朝夕奠讫。必定省于父。虽雨雪不废。服阕。不离父侧。奉养弥笃。父亡。又庐墓三年。哀毁骨立。
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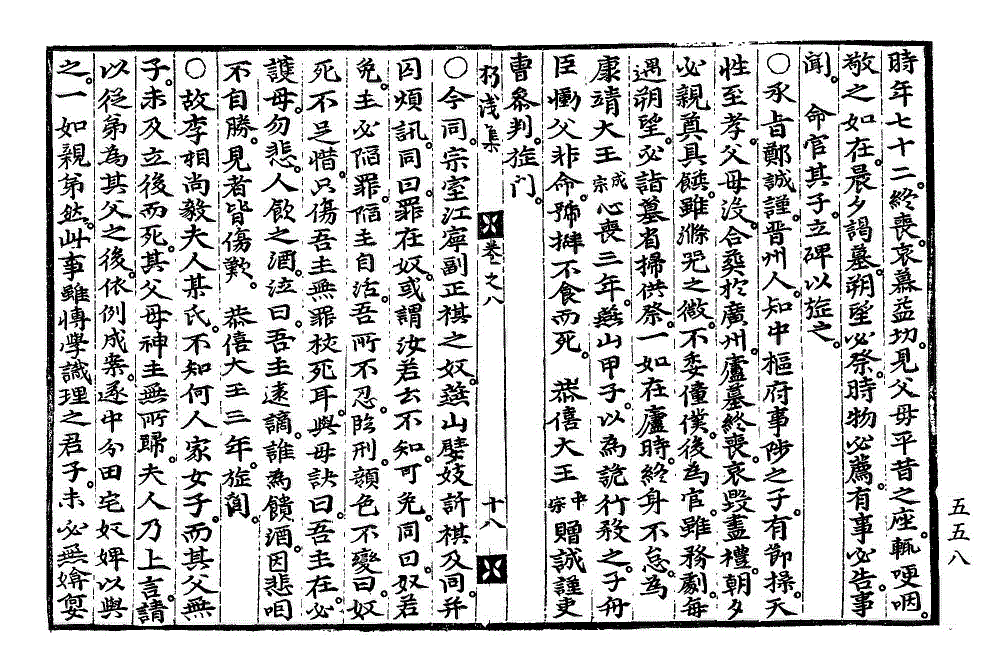 时年七十二。终丧。哀慕益切。见父母平昔之座。辄哽咽。敬之如在。晨夕谒墓。朔望必祭。时物必荐。有事必告。事闻。 命官其子。立碑以旌之。
时年七十二。终丧。哀慕益切。见父母平昔之座。辄哽咽。敬之如在。晨夕谒墓。朔望必祭。时物必荐。有事必告。事闻。 命官其子。立碑以旌之。○承旨郑诚谨。晋州人。知中枢府事陟之子。有节操。天性至孝。父母没。合葬于广州。庐墓终丧。哀毁尽礼。朝夕必亲奠具馔。虽涤器之微。不委僮仆。后为官。虽务剧。每遇朔望。必诣墓省扫供祭。一如在庐时。终身不怠。为 康靖大王(成宗)心丧三年。燕山甲子。以为诡行杀之。子舟臣恸父非命。号擗不食而死。 恭僖大王(中宗)赠诚谨吏曹参判。旌门。
○今同。宗室江宁副正祺之奴。燕山嬖妓䜣祺及同。并囚烦讯。同曰。罪在奴。或谓汝若云不知。可免。同曰。奴若免。主必陷罪。陷主自活。吾所不忍。临刑。颜色不变曰。奴死不足惜。只伤吾主无罪杖死耳。与母诀曰。吾主在。必护母。勿悲。人饮之酒。泣曰。吾主远谪。谁为馈酒。因悲咽不自胜。见者皆伤叹。 恭僖大王三年。旌闾。
○故李相尚毅夫人某氏。不知何人家女子。而其父无子。未及立后而死。其父母神主无所归。夫人乃上言。请以从弟为其父之后。依例成案。遂中分田宅奴婢以与之。一如亲弟然。此事虽博学识理之君子。未必无媕娿
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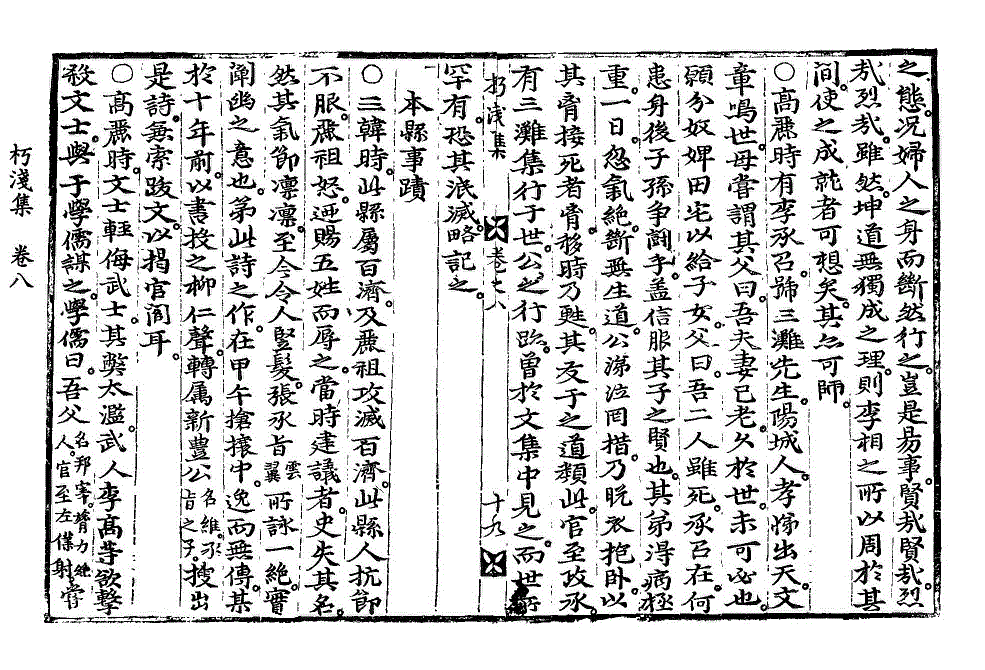 之态。况妇人之身而断然行之。岂是易事。贤哉贤哉。烈哉烈哉。虽然。坤道无独成之理。则李相之所以周于其间。使之成就者可想矣。其亦可师。
之态。况妇人之身而断然行之。岂是易事。贤哉贤哉。烈哉烈哉。虽然。坤道无独成之理。则李相之所以周于其间。使之成就者可想矣。其亦可师。○高丽时有李承召。号三滩先生。阳城人。孝悌出天。文章鸣世。母尝谓其父曰。吾夫妻已老。久于世。未可必也。愿分奴婢田宅以给子女。父曰。吾二人虽死。承召在。何患身后子孙争斗乎。盖信服其子之贤也。其弟得病极重。一日。忽气绝。断无生道。公涕泣罔措。乃脱衣抱卧。以其胸接死者胸。移时乃苏。其友于之道类此。官至政承。有三滩集行子世。公之行迹。曾于文集中见之。而世所罕有。恐其泯灭。略记之。
本县事迹
○三韩时。此县属百济。及丽祖攻灭百济。此县人抗节不服。丽祖怒。乃赐五姓而辱之。当时建议者。史失其名。然其气节凛凛。至今令人竖发。张承旨(云翼)所咏一绝。实阐幽之意也。第此诗之作。在甲午抢攘中。逸而无传。某于十年前。以书投之柳仁声。转属新丰公(名维。承旨之子。)搜出是诗。兼索跋文。以揭官阁耳。
○高丽时。文士轻侮武士。其弊太滥。武人李高等欲击杀文士。与于学儒谋之。学儒曰。吾父(名邦宰。膂力绝人。官至左仆射。)尝
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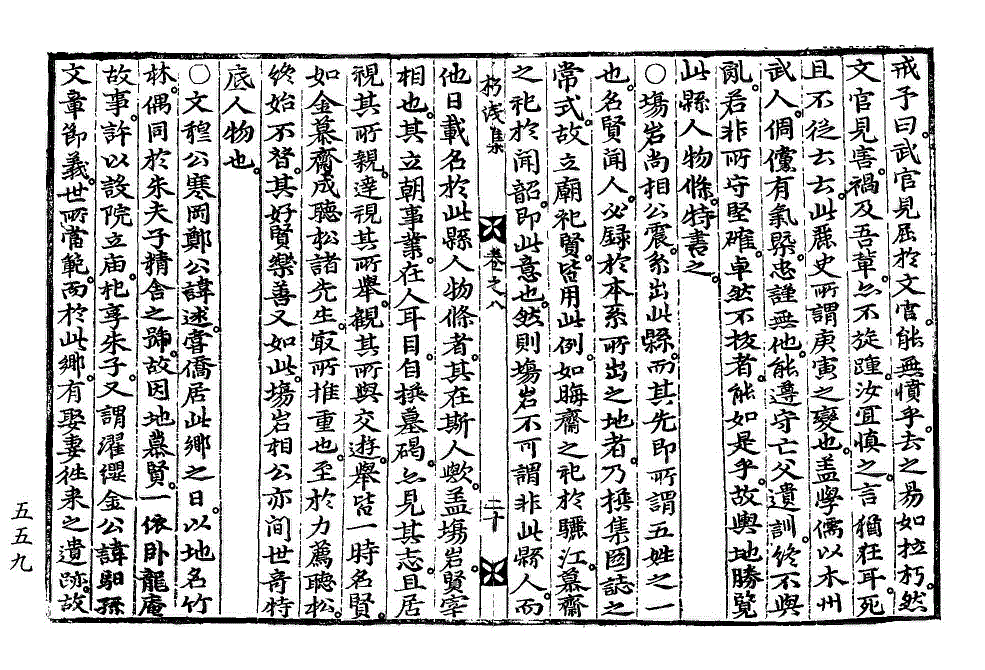 戒予曰。武官见屈于文官。能无愤乎。去之易如拉朽。然文官见害。祸及吾辈。亦不旋踵。汝宜慎之。言犹在耳。死且不从云云。此丽史所谓庚寅之变也。盖学儒以木州武人。倜傥有气槩。忠谨无他。能遵守亡父遗训。终不与乱。若非所守坚确。卓然不拔者。能如是乎。故舆地胜览此县人物条。特书之。
戒予曰。武官见屈于文官。能无愤乎。去之易如拉朽。然文官见害。祸及吾辈。亦不旋踵。汝宜慎之。言犹在耳。死且不从云云。此丽史所谓庚寅之变也。盖学儒以木州武人。倜傥有气槩。忠谨无他。能遵守亡父遗训。终不与乱。若非所守坚确。卓然不拔者。能如是乎。故舆地胜览此县人物条。特书之。○场岩尚相公震。系出此县。而其先即所谓五姓之一也。名贤闻人。必录于本系所出之地者。乃撰集图志之常式。故立庙祀贤。皆用此例。如晦斋之祀于骊江。慕斋之祀于闻韶。即此意也。然则场岩不可谓非此县人。而他日载名于此县人物条者。其在斯人欤。盖场岩。贤宰相也。其立朝事业。在人耳目。自撰墓碣。亦见其志。且居视其所亲。达视其所举。观其所与交游。举皆一时名贤。如金慕斋,成听松诸先生。最所推重也。至于力荐听松。终始不替。其好贤乐善又如此。场岩相公亦间世奇特底人物也。
○文穆公寒冈郑公讳逑。尝侨居此乡之日。以地名竹林。偶同于朱夫子精舍之号。故因地慕贤。一依卧龙庵故事。许以设院立庙。祀享朱子。又谓濯缨金公讳驲孙文章节义。世所当范。而于此乡。有娶妻往来之遗迹。故
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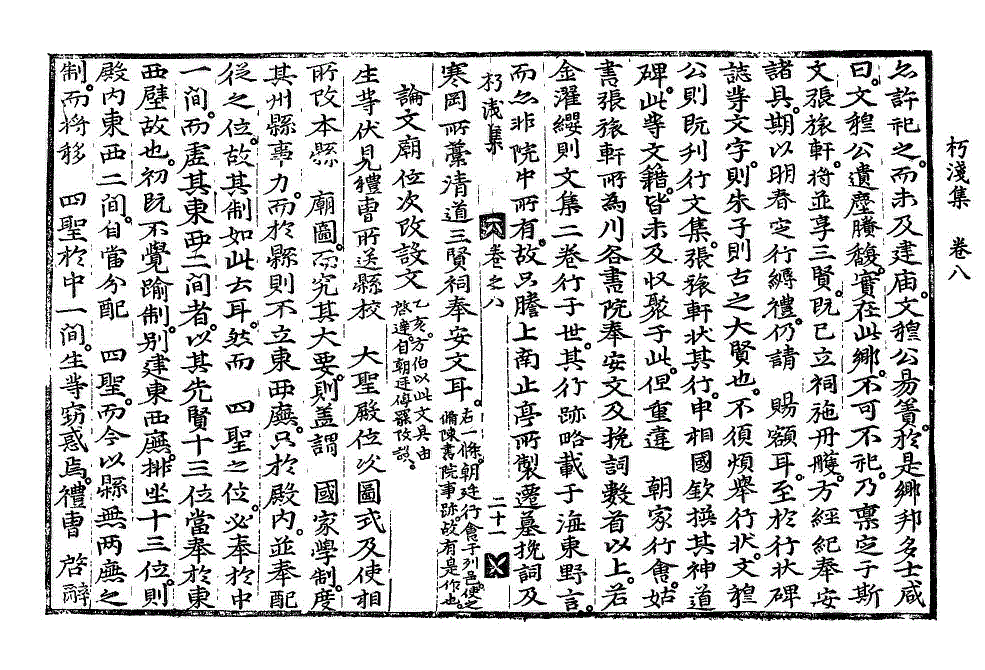 亦许祀之。而未及建庙。文穆公易箦。于是乡邦多士咸曰。文穆公遗尘剩馥。实在此乡。不可不祀。乃禀定于斯文张旅轩。将并享三贤。既已立祠施丹雘。方经纪奉安诸具。期以明春定行缛礼。仍请 赐额耳。至于行状碑志等文字。则朱子则古之大贤也。不须烦举行状。文穆公则既刊行文集。张旅轩状其行。申相国钦撰其神道碑。此等文籍。皆未及收聚于此。但重违 朝家行会。姑书张旅轩所为川谷书院奉安文及挽词数首以上。若金濯缨则文集二卷行于世。其行迹略载于海东野言。而亦非院中所有。故只誊上南止亭所制迁墓挽词及寒冈所稿清道三贤祠奉安文耳。(右一条。朝廷行会于列邑。使之备陈书院事迹。故有是作也。)
亦许祀之。而未及建庙。文穆公易箦。于是乡邦多士咸曰。文穆公遗尘剩馥。实在此乡。不可不祀。乃禀定于斯文张旅轩。将并享三贤。既已立祠施丹雘。方经纪奉安诸具。期以明春定行缛礼。仍请 赐额耳。至于行状碑志等文字。则朱子则古之大贤也。不须烦举行状。文穆公则既刊行文集。张旅轩状其行。申相国钦撰其神道碑。此等文籍。皆未及收聚于此。但重违 朝家行会。姑书张旅轩所为川谷书院奉安文及挽词数首以上。若金濯缨则文集二卷行于世。其行迹略载于海东野言。而亦非院中所有。故只誊上南止亭所制迁墓挽词及寒冈所稿清道三贤祠奉安文耳。(右一条。朝廷行会于列邑。使之备陈书院事迹。故有是作也。)论文庙位次改设文(乙亥。方伯以此文具由启达。自朝廷停罢改设。)
生等伏见礼曹所送县校 大圣殿位次图式及使相所改本县 庙图。而究其大要。则盖谓 国家学制。度其州县事力。而于县则不立东西庑。只于殿内。并奉配从之位。故其制如此云耳。然而 四圣之位。必奉于中一间。而虚其东西二间者。以其先贤十三位当奉于东西壁故也。初既不觉踰制。别建东西庑。排坐十三位。则殿内东西二间。自当分配 四圣。而今以县无两庑之制。而将移 四圣于中一间。生等窃惑焉。礼曹 启辞
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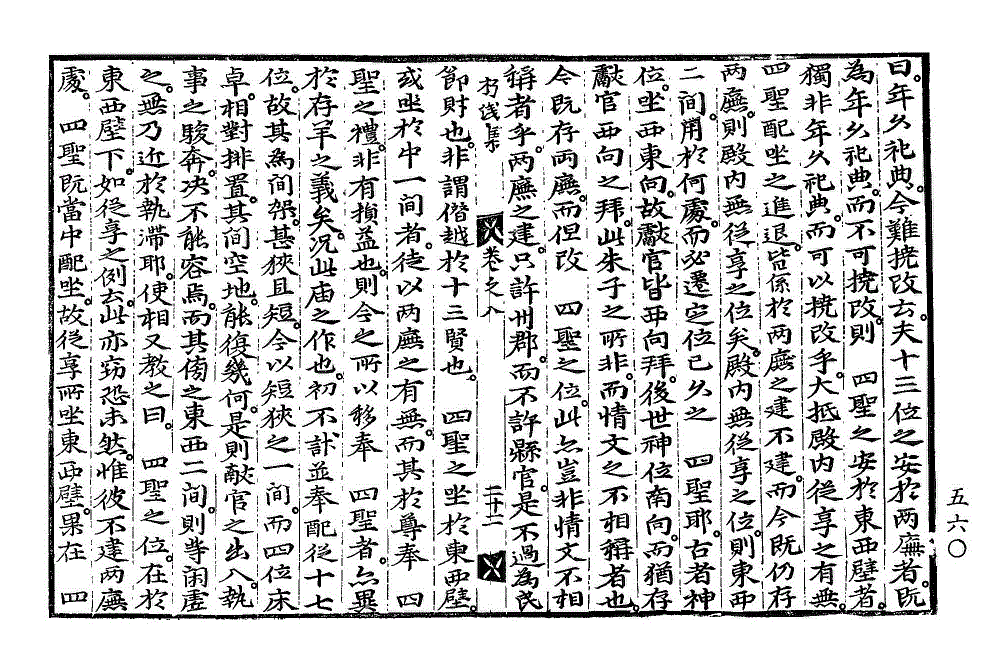 曰。年久祀典。今难挠改云。夫十三位之安于两庑者。既为年久祀典。而不可挠改。则 四圣之安于东西壁者。独非年久祀典。而可以挠改乎。大抵殿内从享之有无。四圣配坐之进退。皆系于两庑之建不建。而今既仍存两庑。则殿内无从享之位矣。殿内无从享之位。则东西二间。用于何处。而必迁定位已久之 四圣耶。古者神位。坐西东向。故献官皆西向拜。后世神位南向。而犹存献官西向之拜。此朱子之所非。而情文之不相称者也。今既存两庑。而但改 四圣之位。此亦岂非情文不相称者乎。两庑之建。只许州郡。而不许县官。是不过为民节财也。非谓僭越于十三贤也。 四圣之坐于东西壁。或坐于中一间者。徒以两庑之有无。而其于尊奉 四圣之礼。非有损益也。则今之所以移奉 四圣者。亦异于存羊之义矣。况此庙之作也。初不计并奉配从十七位。故其为间架。甚狭且短。今以短狭之一间。而四位床卓。相对排置。其间空地。能复几何。是则献官之出入。执事之骏奔。决不能容焉。而其傍之东西二间。则等闲虚之。无乃近于执滞耶。使相又教之曰。 四圣之位。在于东西壁下。如从享之例云。此亦窃恐未然。惟彼不建两庑处。 四圣既当中配坐。故从享所坐东西壁。果在 四
曰。年久祀典。今难挠改云。夫十三位之安于两庑者。既为年久祀典。而不可挠改。则 四圣之安于东西壁者。独非年久祀典。而可以挠改乎。大抵殿内从享之有无。四圣配坐之进退。皆系于两庑之建不建。而今既仍存两庑。则殿内无从享之位矣。殿内无从享之位。则东西二间。用于何处。而必迁定位已久之 四圣耶。古者神位。坐西东向。故献官皆西向拜。后世神位南向。而犹存献官西向之拜。此朱子之所非。而情文之不相称者也。今既存两庑。而但改 四圣之位。此亦岂非情文不相称者乎。两庑之建。只许州郡。而不许县官。是不过为民节财也。非谓僭越于十三贤也。 四圣之坐于东西壁。或坐于中一间者。徒以两庑之有无。而其于尊奉 四圣之礼。非有损益也。则今之所以移奉 四圣者。亦异于存羊之义矣。况此庙之作也。初不计并奉配从十七位。故其为间架。甚狭且短。今以短狭之一间。而四位床卓。相对排置。其间空地。能复几何。是则献官之出入。执事之骏奔。决不能容焉。而其傍之东西二间。则等闲虚之。无乃近于执滞耶。使相又教之曰。 四圣之位。在于东西壁下。如从享之例云。此亦窃恐未然。惟彼不建两庑处。 四圣既当中配坐。故从享所坐东西壁。果在 四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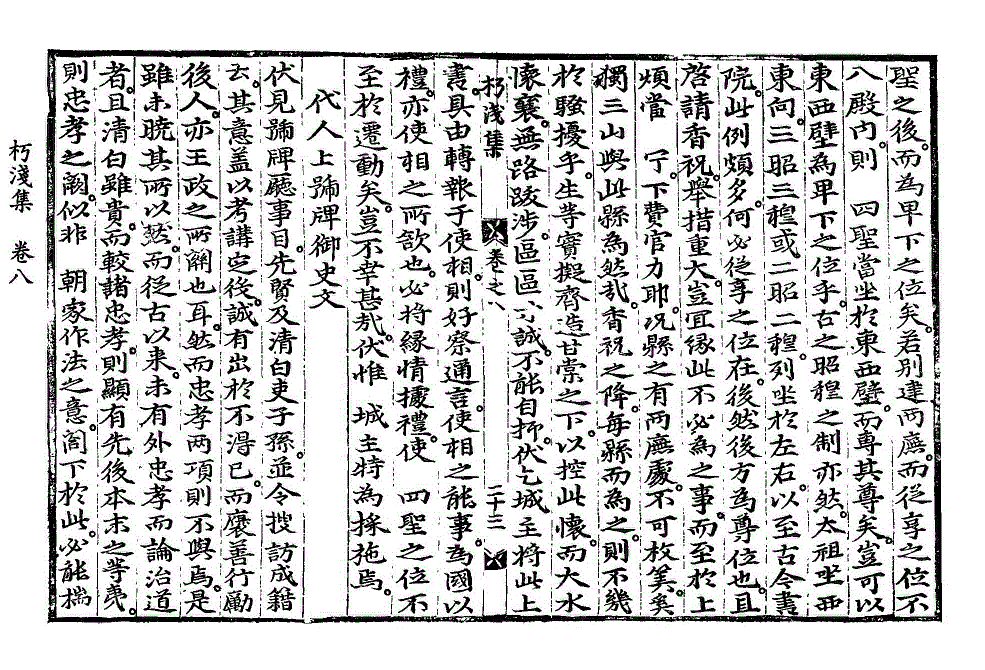 圣之后。而为早下之位矣。若别建两庑。而从享之位不入殿内。则 四圣当坐于东西壁。而专其尊矣。岂可以东西壁为卑下之位乎。古之昭穆之制亦然。太祖坐西东向。三昭三穆或二昭二穆。列坐于左右。以至古今书院。此例颇多。何必从享之位在。后然后方为尊位也。且启请香祝。举措重大。岂宜缘此不必为之事。而至于上烦当 宁。下费官力耶。况县之有两庑处。不可枚算。奚独三山与此县为然哉。香祝之降。每县而为之。则不几于骚扰乎。生等实拟齐造甘棠之下。以控此怀。而大水怀襄。无路跋涉。区区寸诚。不能自抑。伏乞城主将此上书。具由转报于使相。则好察迩言。使相之能事。为国以礼。亦使相之所欲也。必将缘情据礼。使 四圣之位不至于迁动矣。岂不幸甚哉。伏惟 城主特为采施焉。
圣之后。而为早下之位矣。若别建两庑。而从享之位不入殿内。则 四圣当坐于东西壁。而专其尊矣。岂可以东西壁为卑下之位乎。古之昭穆之制亦然。太祖坐西东向。三昭三穆或二昭二穆。列坐于左右。以至古今书院。此例颇多。何必从享之位在。后然后方为尊位也。且启请香祝。举措重大。岂宜缘此不必为之事。而至于上烦当 宁。下费官力耶。况县之有两庑处。不可枚算。奚独三山与此县为然哉。香祝之降。每县而为之。则不几于骚扰乎。生等实拟齐造甘棠之下。以控此怀。而大水怀襄。无路跋涉。区区寸诚。不能自抑。伏乞城主将此上书。具由转报于使相。则好察迩言。使相之能事。为国以礼。亦使相之所欲也。必将缘情据礼。使 四圣之位不至于迁动矣。岂不幸甚哉。伏惟 城主特为采施焉。代人上号牌御史文
伏见号牌厅事目。先贤及清白吏子孙。并令搜访成籍云。其意盖以考讲定役。诚有出于不得已。而褒善行励后人。亦王政之所关也耳。然而忠孝两项则不与焉。是虽未晓其所以然。而从古以来。未有外忠孝而论治道者。且清白虽贵。而较诸忠孝。则显有先后本末之等夷。则忠孝之阙。似非 朝家作法之意。阁下于此。必能揣
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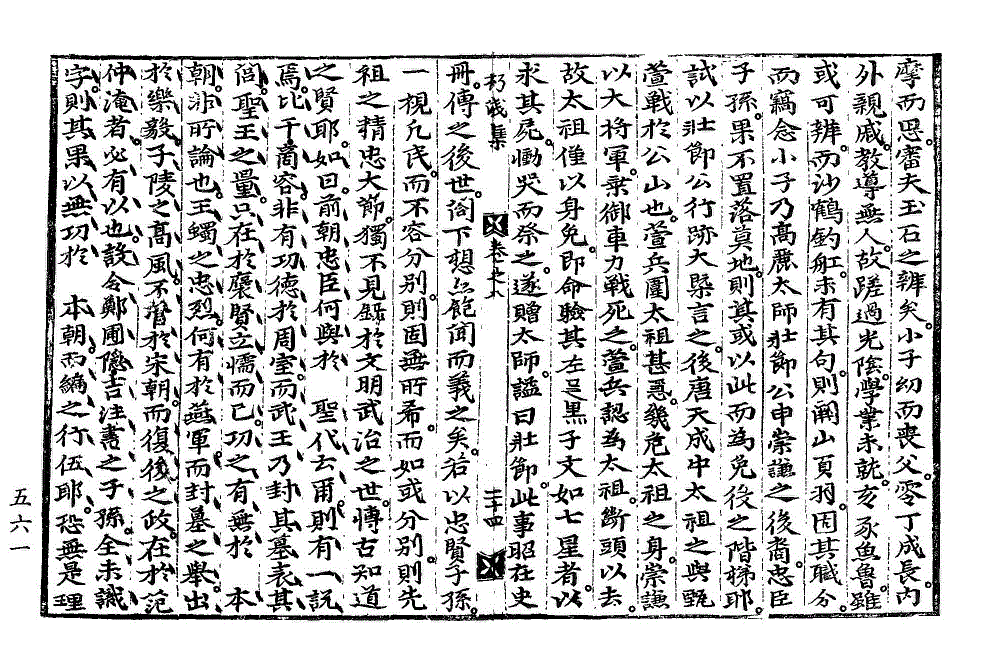 摩而思。审夫玉石之辨矣。小子幼而丧父。零丁成长。内外亲戚。教导燕人。故蹉过光阴。学业未就。亥豕鱼鲁。虽或可辨。而沙鹤钓舡。未有其句。则关山页羽。固其职分。而窃念小子乃高丽太师壮节公申崇谦之后裔。忠臣子孙。果不置落莫地。则其或以此而为免役之阶梯耶。试以壮节公行迹大槩言之。后唐天成中太祖之与甄萱战于公山也。萱兵围太祖甚急。几危太祖之身。崇谦以大将军。乘御车力战死之。萱兵认为太祖。断头以去。故太祖仅以身免。即命验其左足黑子文如七星者。以求其尸。恸哭而祭之。遂赠太师。谥曰壮节。此事昭在史册。传之后世。閤下想亦饱闻而义之矣。若以忠贤子孙。一视凡民。而不容分别。则固无所希。而如或分别。则先祖之精忠大节。独不见录于文明武治之世。博古知道之贤耶。【如曰。前朝忠臣何与于 圣代云尔。则有一说焉。比干,商容。非有功德于周室。而武王乃封其墓表其闾。圣王之量。只在于褒贤立懦而已。功之有无于 本朝。非所论也。王蠋之忠烈。何有于燕军。而封墓之举。出于乐毅。子陵之高风。不管于宋朝。而复后之政。在于范仲淹者。必有以也。设令郑圃隐,吉注书之子孙。全未识字。则其果以无功于 本朝。而编之行伍耶。】恐无是理
摩而思。审夫玉石之辨矣。小子幼而丧父。零丁成长。内外亲戚。教导燕人。故蹉过光阴。学业未就。亥豕鱼鲁。虽或可辨。而沙鹤钓舡。未有其句。则关山页羽。固其职分。而窃念小子乃高丽太师壮节公申崇谦之后裔。忠臣子孙。果不置落莫地。则其或以此而为免役之阶梯耶。试以壮节公行迹大槩言之。后唐天成中太祖之与甄萱战于公山也。萱兵围太祖甚急。几危太祖之身。崇谦以大将军。乘御车力战死之。萱兵认为太祖。断头以去。故太祖仅以身免。即命验其左足黑子文如七星者。以求其尸。恸哭而祭之。遂赠太师。谥曰壮节。此事昭在史册。传之后世。閤下想亦饱闻而义之矣。若以忠贤子孙。一视凡民。而不容分别。则固无所希。而如或分别。则先祖之精忠大节。独不见录于文明武治之世。博古知道之贤耶。【如曰。前朝忠臣何与于 圣代云尔。则有一说焉。比干,商容。非有功德于周室。而武王乃封其墓表其闾。圣王之量。只在于褒贤立懦而已。功之有无于 本朝。非所论也。王蠋之忠烈。何有于燕军。而封墓之举。出于乐毅。子陵之高风。不管于宋朝。而复后之政。在于范仲淹者。必有以也。设令郑圃隐,吉注书之子孙。全未识字。则其果以无功于 本朝。而编之行伍耶。】恐无是理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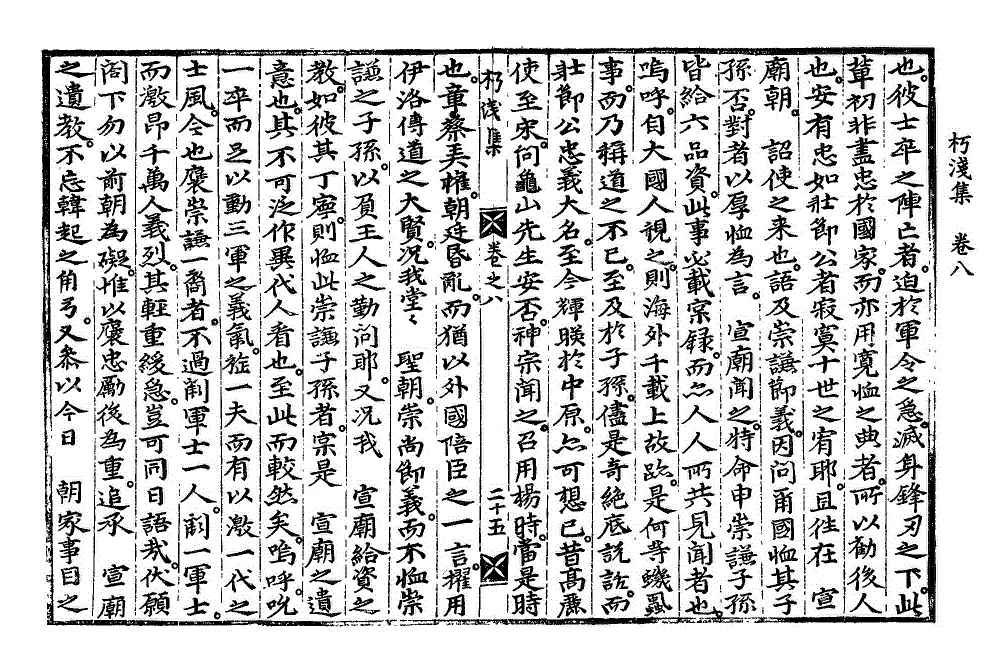 也。彼士卒之阵亡者。迫于军令之急。灭身锋刃之下。此辈初非尽忠于国家。而亦用宽恤之典者。所以劝后人也。安有忠如壮节公者寂寞十世之宥耶。且往在 宣庙朝。 诏使之来也。语及崇谦节义。因问尔国恤其子孙否。对者以厚恤为言。 宣庙闻之。特命申崇谦子孙皆给六品资。此事必载实录。而亦人人所共见闻者也。呜呼。自大国人视之。则海外千载上故迹。是何等虮虱事。而乃称道之不已。至及于子孙。尽是奇绝底说话。而壮节公忠义大名。至今辉映于中原。亦可想已。昔高丽使至宋。问龟山先生安否。神宗闻之。召用杨时。当是时也。章,蔡弄权。朝廷昏乱。而犹以外国陪臣之一言。擢用伊洛传道之大贤。况我堂堂 圣朝。崇尚节义。而不恤崇谦之子孙。以负王人之勤问耶。又况我 宣庙给资之教。如彼其丁宁。则恤此崇谦子孙者。实是 宣庙之遗意也。其不可泛作异代人看也。至此而较然矣。呜呼。吮一卒而足以动三军之义气。旌一夫而有以激一代之士风。今也褒崇谦一裔者。不过阙军士一人。阙一军士。而激昂千万人义烈。其轻重缓急。岂可同日语哉。伏愿閤下勿以前朝为碍。惟以褒忠励后为重。追承 宣庙之遗教。不忘韩起之角弓。又参以今日 朝家事目之
也。彼士卒之阵亡者。迫于军令之急。灭身锋刃之下。此辈初非尽忠于国家。而亦用宽恤之典者。所以劝后人也。安有忠如壮节公者寂寞十世之宥耶。且往在 宣庙朝。 诏使之来也。语及崇谦节义。因问尔国恤其子孙否。对者以厚恤为言。 宣庙闻之。特命申崇谦子孙皆给六品资。此事必载实录。而亦人人所共见闻者也。呜呼。自大国人视之。则海外千载上故迹。是何等虮虱事。而乃称道之不已。至及于子孙。尽是奇绝底说话。而壮节公忠义大名。至今辉映于中原。亦可想已。昔高丽使至宋。问龟山先生安否。神宗闻之。召用杨时。当是时也。章,蔡弄权。朝廷昏乱。而犹以外国陪臣之一言。擢用伊洛传道之大贤。况我堂堂 圣朝。崇尚节义。而不恤崇谦之子孙。以负王人之勤问耶。又况我 宣庙给资之教。如彼其丁宁。则恤此崇谦子孙者。实是 宣庙之遗意也。其不可泛作异代人看也。至此而较然矣。呜呼。吮一卒而足以动三军之义气。旌一夫而有以激一代之士风。今也褒崇谦一裔者。不过阙军士一人。阙一军士。而激昂千万人义烈。其轻重缓急。岂可同日语哉。伏愿閤下勿以前朝为碍。惟以褒忠励后为重。追承 宣庙之遗教。不忘韩起之角弓。又参以今日 朝家事目之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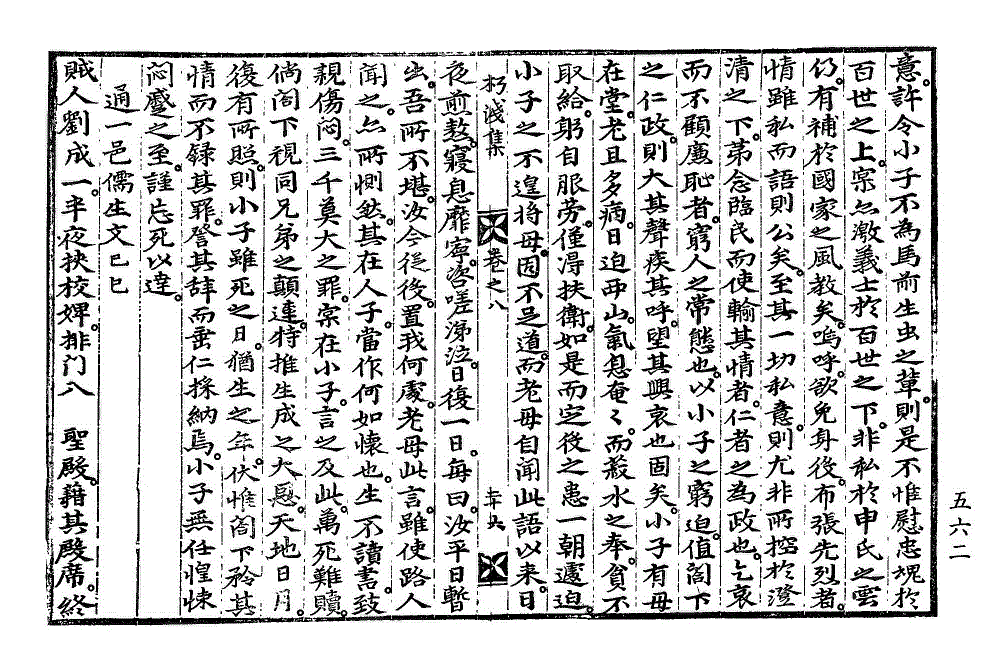 意。许令小子不为马前生虫之辈。则是不惟慰忠魂于百世之上。实亦激义士于百世之下。非私于申氏之云仍。有补于国家之风教矣。呜呼。欲免身役。布张先烈者。情虽私而语则公矣。至其一切私意。则尤非所控于澄清之下。第念临民而使输其情者。仁者之为政也。乞哀而不顾廉耻者。穷人之常态也。以小子之穷迫。值閤下之仁政。则大其声疾其呼。望其兴哀也固矣。小子有母在堂。老且多病。日迫西山。气息奄奄。而蔽水之奉。贫不取给。躬自服劳。仅得扶卫。如是而定役之患一朝遽迫。小子之不遑将母。固不足道。而老母自闻此语以来。日夜煎熬。寝息靡宁。咨嗟涕泣。日复一日。每曰。汝平日暂出。吾所不堪。汝今从役。置我何处。老母此言。虽使路人闻之。亦所恻然。其在人子。当作何如怀也。生不读书。致亲伤闷。三千莫大之罪。实在小子。言之及此。万死难赎。倘閤下视同兄弟之颠连。特推生成之大恩。天地日月。复有所照。则小子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伏惟閤下矜其情而不录其罪。察其辞而垂仁采纳焉。小子无任惶悚闷蹙之至。谨忘死以达。
意。许令小子不为马前生虫之辈。则是不惟慰忠魂于百世之上。实亦激义士于百世之下。非私于申氏之云仍。有补于国家之风教矣。呜呼。欲免身役。布张先烈者。情虽私而语则公矣。至其一切私意。则尤非所控于澄清之下。第念临民而使输其情者。仁者之为政也。乞哀而不顾廉耻者。穷人之常态也。以小子之穷迫。值閤下之仁政。则大其声疾其呼。望其兴哀也固矣。小子有母在堂。老且多病。日迫西山。气息奄奄。而蔽水之奉。贫不取给。躬自服劳。仅得扶卫。如是而定役之患一朝遽迫。小子之不遑将母。固不足道。而老母自闻此语以来。日夜煎熬。寝息靡宁。咨嗟涕泣。日复一日。每曰。汝平日暂出。吾所不堪。汝今从役。置我何处。老母此言。虽使路人闻之。亦所恻然。其在人子。当作何如怀也。生不读书。致亲伤闷。三千莫大之罪。实在小子。言之及此。万死难赎。倘閤下视同兄弟之颠连。特推生成之大恩。天地日月。复有所照。则小子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伏惟閤下矜其情而不录其罪。察其辞而垂仁采纳焉。小子无任惶悚闷蹙之至。谨忘死以达。通一邑儒生文(己巳)
贼人刘成一。半夜挟校婢。排门入 圣殿。藉其殿席。终
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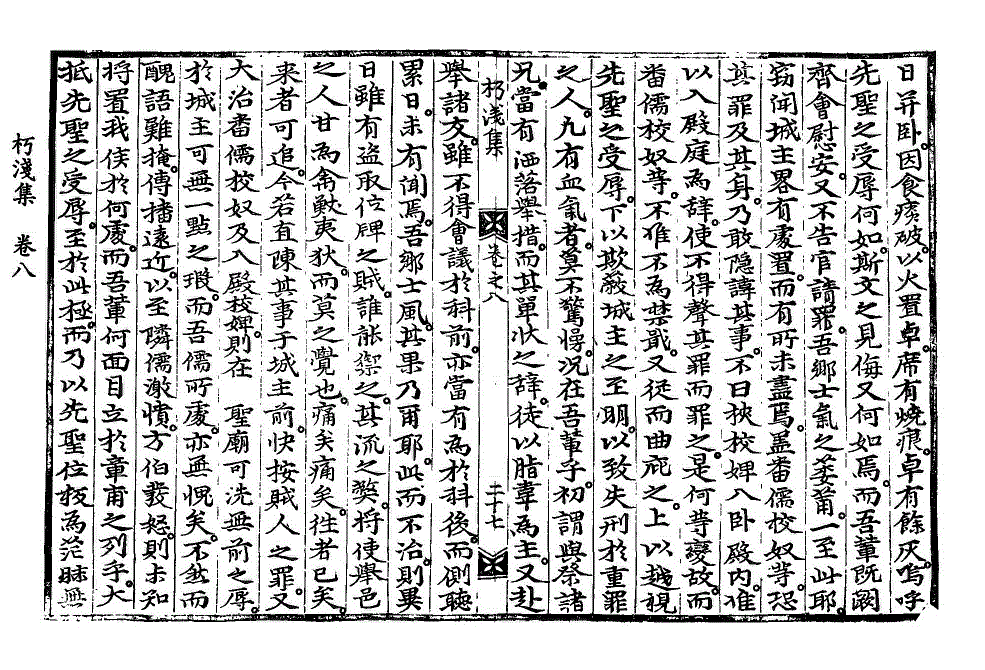 日并卧。因食痰破。以火置卓。席有烧痕。卓有馀灰。呜呼先圣之受辱何如。斯文之见侮又何如焉。而吾辈既阙齐会慰安。又不告官请罪。吾乡士气之萎莆。一至此耶。窃闻城主略有处置。而有所未尽焉。盖番儒校奴等。恐其罪及其身。乃敢隐讳其事。不日挟校婢入卧殿内。惟以入殿庭为辞。使不得声其罪而罪之。是何等变故。而番儒校奴等。不惟不为禁戢。又从而曲庇之。上以越视先圣之受辱。下以欺蔽城主之至明。以致失刑于重罪之人。凡有血气者。莫不惊愕。况在吾辈乎。初谓与祭诸兄。当有洒落举措。而其单状之辞。徒以脂韦为主。又赴举诸友。虽不得会议于科前。亦当有为于科后。而侧听累日。未有闻焉。吾乡士风。其果乃尔耶。此而不治。则异日虽有盗取位牌之贼。谁能御之。其流之弊。将使举邑之人甘为禽兽夷狄。而莫之觉也。痛矣痛矣。往者已矣。来者可追。今若直陈其事于城主前。快按贼人之罪。又大治番儒校奴及入殿校婢。则在 圣庙可洗无前之辱。于城主可无一点之瑕。而吾儒所处。亦无愧矣。不然而丑语难掩。传播远近。以至邻儒激愤。方伯发怒。则未知将置我侯于何处。而吾辈何面目立于章甫之列乎。大抵先圣之受辱。至于此极。而乃以先圣位板为茫昧无
日并卧。因食痰破。以火置卓。席有烧痕。卓有馀灰。呜呼先圣之受辱何如。斯文之见侮又何如焉。而吾辈既阙齐会慰安。又不告官请罪。吾乡士气之萎莆。一至此耶。窃闻城主略有处置。而有所未尽焉。盖番儒校奴等。恐其罪及其身。乃敢隐讳其事。不日挟校婢入卧殿内。惟以入殿庭为辞。使不得声其罪而罪之。是何等变故。而番儒校奴等。不惟不为禁戢。又从而曲庇之。上以越视先圣之受辱。下以欺蔽城主之至明。以致失刑于重罪之人。凡有血气者。莫不惊愕。况在吾辈乎。初谓与祭诸兄。当有洒落举措。而其单状之辞。徒以脂韦为主。又赴举诸友。虽不得会议于科前。亦当有为于科后。而侧听累日。未有闻焉。吾乡士风。其果乃尔耶。此而不治。则异日虽有盗取位牌之贼。谁能御之。其流之弊。将使举邑之人甘为禽兽夷狄。而莫之觉也。痛矣痛矣。往者已矣。来者可追。今若直陈其事于城主前。快按贼人之罪。又大治番儒校奴及入殿校婢。则在 圣庙可洗无前之辱。于城主可无一点之瑕。而吾儒所处。亦无愧矣。不然而丑语难掩。传播远近。以至邻儒激愤。方伯发怒。则未知将置我侯于何处。而吾辈何面目立于章甫之列乎。大抵先圣之受辱。至于此极。而乃以先圣位板为茫昧无朽浅先生集卷之八 第 5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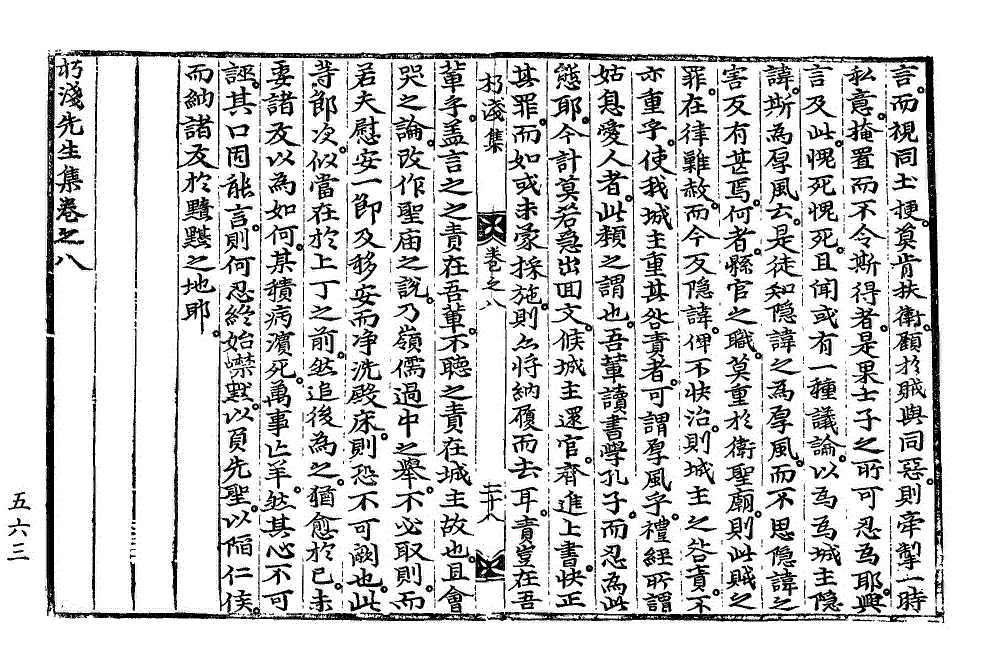 言。而视同土梗。莫肯扶卫。顾于贼与同恶。则牵掣一时私意。掩置而不令斯得者。是果士子之所可忍为耶。兴言及此。愧死愧死。且闻或有一种议论。以为为城主隐讳。斯为厚风云。是徒知隐讳之为厚风。而不思隐讳之害反有甚焉。何者。县官之职。莫重于卫圣庙。则此贼之罪。在律杂赦。而今反隐讳。俾不快治。则城主之咎责。不亦重乎。使我城主重其咎责者。可谓厚风乎。礼经所谓姑息爱人者。此类之谓也。吾辈读书学孔子。而忍为此态耶。今计莫若急出回文。候城主还官。齐进上书。快正其罪。而如或未蒙采施。则亦将纳履而去耳。责岂在吾辈乎。盖言之之责在吾辈。不听之责在城主故也。且会哭之论。改作圣庙之说。乃岭儒过中之举。不必取则。而若夫慰安一节及移安而净洗殿床。则恐不可阙也。此等节次。似当在于上丁之前。然追后为之。犹愈于己。未要诸友以为如何。某积病滨死。万事亡羊。然其心不可诬。其口固能言。则何忍终始噤默。以负先圣。以陷仁侯。而纳诸友于黯黮之地耶。
言。而视同土梗。莫肯扶卫。顾于贼与同恶。则牵掣一时私意。掩置而不令斯得者。是果士子之所可忍为耶。兴言及此。愧死愧死。且闻或有一种议论。以为为城主隐讳。斯为厚风云。是徒知隐讳之为厚风。而不思隐讳之害反有甚焉。何者。县官之职。莫重于卫圣庙。则此贼之罪。在律杂赦。而今反隐讳。俾不快治。则城主之咎责。不亦重乎。使我城主重其咎责者。可谓厚风乎。礼经所谓姑息爱人者。此类之谓也。吾辈读书学孔子。而忍为此态耶。今计莫若急出回文。候城主还官。齐进上书。快正其罪。而如或未蒙采施。则亦将纳履而去耳。责岂在吾辈乎。盖言之之责在吾辈。不听之责在城主故也。且会哭之论。改作圣庙之说。乃岭儒过中之举。不必取则。而若夫慰安一节及移安而净洗殿床。则恐不可阙也。此等节次。似当在于上丁之前。然追后为之。犹愈于己。未要诸友以为如何。某积病滨死。万事亡羊。然其心不可诬。其口固能言。则何忍终始噤默。以负先圣。以陷仁侯。而纳诸友于黯黮之地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