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疏庵先生集卷之三 第 x 页
疏庵先生集卷之三
赋
赋
疏庵先生集卷之三 第 4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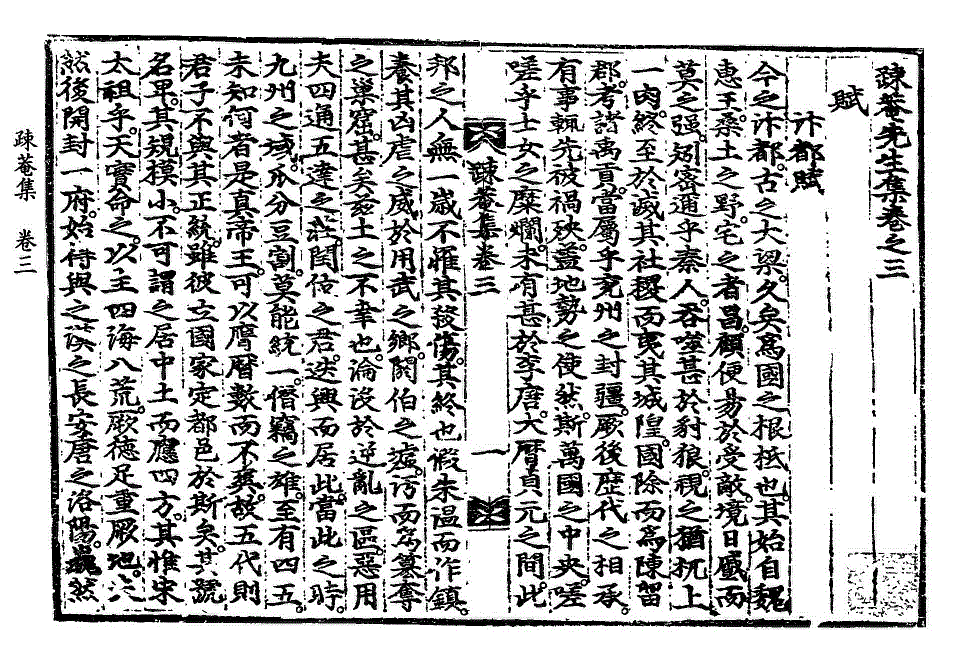 汴都赋
汴都赋今之汴都。古之大梁。久矣为国之根柢也。其始自魏惠王。桑土之野。宅之者昌。顾便易于受敌。境日蹙而莫之强。矧密迩乎秦人。吞噬甚于豺狼。视之犹杌上一肉。终至于灭其社稷而夷其城隍。国除而为陈留郡。考诸禹贡。当属乎兖州之封疆。厥后历代之相承。有事辄先被祸殃。盖地势之使然。斯万国之中央。嗟嗟乎士女之糜烂。未有甚于李唐。大历,贞元之间。此邦之人无一岁不罹其杀伤。其终也假朱温而作镇。养其凶虐之威于用武之乡。阏伯之墟。污而为篡夺之巢窟。甚矣兹土之不幸也。沦没于逆乱之区。恶用夫四通五达之庄。闰位之君。迭兴而居此。当此之时。九州之域。瓜分豆割。莫能统一。僭窃之雄。至有四五。未知何者是真帝王。可以膺历数而不爽。故五代则君子不与其正统。虽彼立国家定都邑于斯矣。其号名卑。其规模小。不可谓之居中土而应四方。其惟宋太祖乎。天实命之。以主四海八荒。厥德足重厥地。夫然后开封一府。始侍与之汉之长安唐之洛阳。巍然
疏庵先生集卷之三 第 4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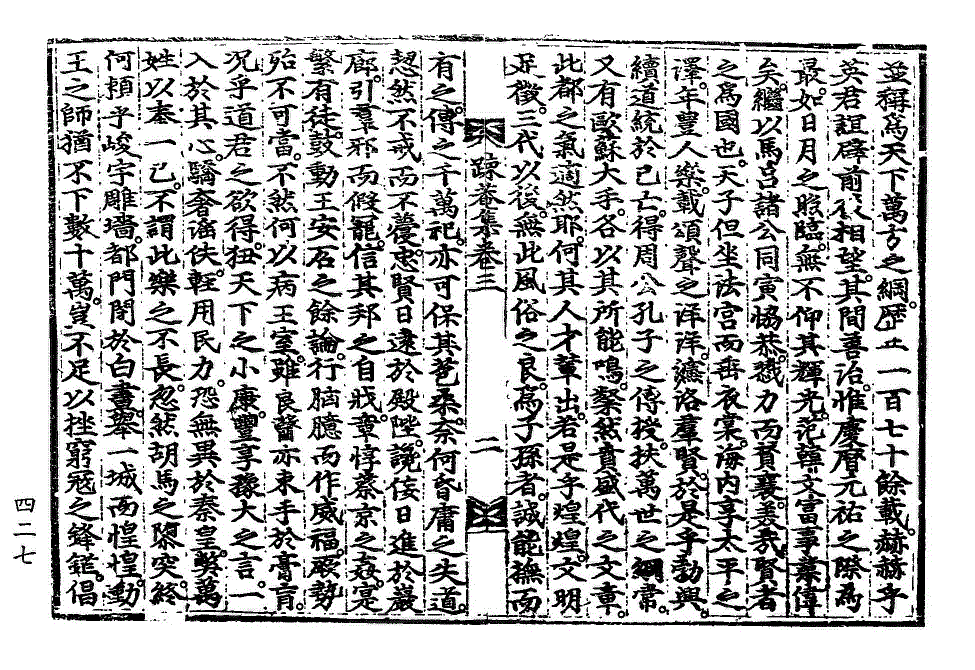 并称为天下万方之纲。历一百七十馀载。赫赫乎英君谊辟前后相望。其间善治。惟庆历,元祐之际为最。如日月之照临。无不仰其辉光。范,韩,文,富事业伟矣。继以马,吕诸公同寅协恭。戮力而赞襄。美哉贤者之为国也。天子但坐法宫而垂衣裳。海内享太平之泽。年丰人乐。载颂声之洋洋。濂洛群贤。于是乎勃兴。续道统于已亡。得周公孔子之传授。扶万世之纲常。又有欧,苏大手。各以其所能鸣。粲然贲盛代之文章。此都之气适然耶。何其人才辈出。若是乎煌煌。文明足徵。三代以后。无此风俗之良。为子孙者。诚能抚而有之。传之千万祀。亦可保其苞桑。奈何昏庸之失道。恝然不戒而不蘉。忠贤日远于殿陛。谗佞日进于岩廊。引群邪而假宠。信其邦之自戕。章惇蔡京之奸。寔繁有徒。鼓动王安石之馀论。行脑臆而作威福。厥势殆不可当。不然何以病王室。虽良医亦束手于膏肓。况乎道君之欲得。狃天下之小康。丰享豫大之言。一入于其心。骄奢淫佚。轻用民力。恐无异于秦皇。弊万姓以奉一已。不谓此乐之不长。忽然胡马之隳突。终何赖乎峻宇雕墙。都门闭于白昼。举一城而惶惶。勤王之师犹不下数十万。岂不足以挫穷寇之锋铓。倡
并称为天下万方之纲。历一百七十馀载。赫赫乎英君谊辟前后相望。其间善治。惟庆历,元祐之际为最。如日月之照临。无不仰其辉光。范,韩,文,富事业伟矣。继以马,吕诸公同寅协恭。戮力而赞襄。美哉贤者之为国也。天子但坐法宫而垂衣裳。海内享太平之泽。年丰人乐。载颂声之洋洋。濂洛群贤。于是乎勃兴。续道统于已亡。得周公孔子之传授。扶万世之纲常。又有欧,苏大手。各以其所能鸣。粲然贲盛代之文章。此都之气适然耶。何其人才辈出。若是乎煌煌。文明足徵。三代以后。无此风俗之良。为子孙者。诚能抚而有之。传之千万祀。亦可保其苞桑。奈何昏庸之失道。恝然不戒而不蘉。忠贤日远于殿陛。谗佞日进于岩廊。引群邪而假宠。信其邦之自戕。章惇蔡京之奸。寔繁有徒。鼓动王安石之馀论。行脑臆而作威福。厥势殆不可当。不然何以病王室。虽良医亦束手于膏肓。况乎道君之欲得。狃天下之小康。丰享豫大之言。一入于其心。骄奢淫佚。轻用民力。恐无异于秦皇。弊万姓以奉一已。不谓此乐之不长。忽然胡马之隳突。终何赖乎峻宇雕墙。都门闭于白昼。举一城而惶惶。勤王之师犹不下数十万。岂不足以挫穷寇之锋铓。倡疏庵先生集卷之三 第 4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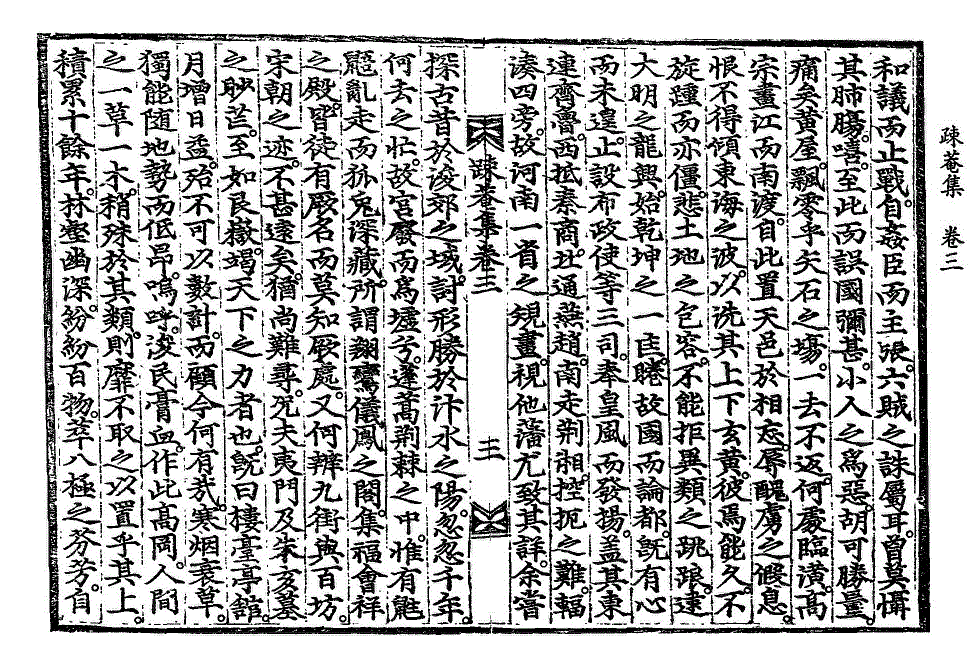 和议而止战。自奸臣而主张。六贼之诛属耳。曾莫慑其肺肠。嘻。至此而误国弥甚。小人之为恶。胡可胜量。痛矣黄屋。飘零乎矢石之场。一去不返。何处临潢。高宗画江而南渡。自此置天邑于相忘。辱丑虏之假息。恨不得倾东海之波。以洗其上下玄黄。彼焉能久。不旋踵而亦僵。悲土地之包容。不能拒异类之跳踉。逮大明之龙兴。始乾坤之一匡。眷故国而论都。既有心而未遑。止设布政使等三司。奉皇风而发扬。盖其东连齐鲁。西抵秦商。北通燕赵。南走荆湘。控扼之难。辐凑四旁。故河南一省之规画。视他藩尤致其详。余尝探古昔于浚郊之域。讨形胜于汴水之阳。忽忽千年。何去之忙。故宫废而为墟兮。蓬蒿荆棘之中。惟有鼪鼯乱走而狐兔深藏。所谓翔鸾仪凤之阁。集福会祥之殿。皆徒有厥名而莫知厥处。又何辨九街与百坊。宋朝之迹。不甚远矣。犹尚难寻。况夫夷门及朱亥墓之眇芒。至如艮岳。竭天下之力者也。既曰楼台亭馆。月增日益。殆不可以数计。而顾今何有哉。寒烟衰草。独能随地势而低昂。呜呼。浚民膏血。作此高冈。人间之一草一木。稍殊于其类。则靡不取之以置乎其上。积累十馀年。林壑幽深。纷纷百物萃八极之芬芳。自
和议而止战。自奸臣而主张。六贼之诛属耳。曾莫慑其肺肠。嘻。至此而误国弥甚。小人之为恶。胡可胜量。痛矣黄屋。飘零乎矢石之场。一去不返。何处临潢。高宗画江而南渡。自此置天邑于相忘。辱丑虏之假息。恨不得倾东海之波。以洗其上下玄黄。彼焉能久。不旋踵而亦僵。悲土地之包容。不能拒异类之跳踉。逮大明之龙兴。始乾坤之一匡。眷故国而论都。既有心而未遑。止设布政使等三司。奉皇风而发扬。盖其东连齐鲁。西抵秦商。北通燕赵。南走荆湘。控扼之难。辐凑四旁。故河南一省之规画。视他藩尤致其详。余尝探古昔于浚郊之域。讨形胜于汴水之阳。忽忽千年。何去之忙。故宫废而为墟兮。蓬蒿荆棘之中。惟有鼪鼯乱走而狐兔深藏。所谓翔鸾仪凤之阁。集福会祥之殿。皆徒有厥名而莫知厥处。又何辨九街与百坊。宋朝之迹。不甚远矣。犹尚难寻。况夫夷门及朱亥墓之眇芒。至如艮岳。竭天下之力者也。既曰楼台亭馆。月增日益。殆不可以数计。而顾今何有哉。寒烟衰草。独能随地势而低昂。呜呼。浚民膏血。作此高冈。人间之一草一木。稍殊于其类。则靡不取之以置乎其上。积累十馀年。林壑幽深。纷纷百物萃八极之芬芳。自疏庵先生集卷之三 第 4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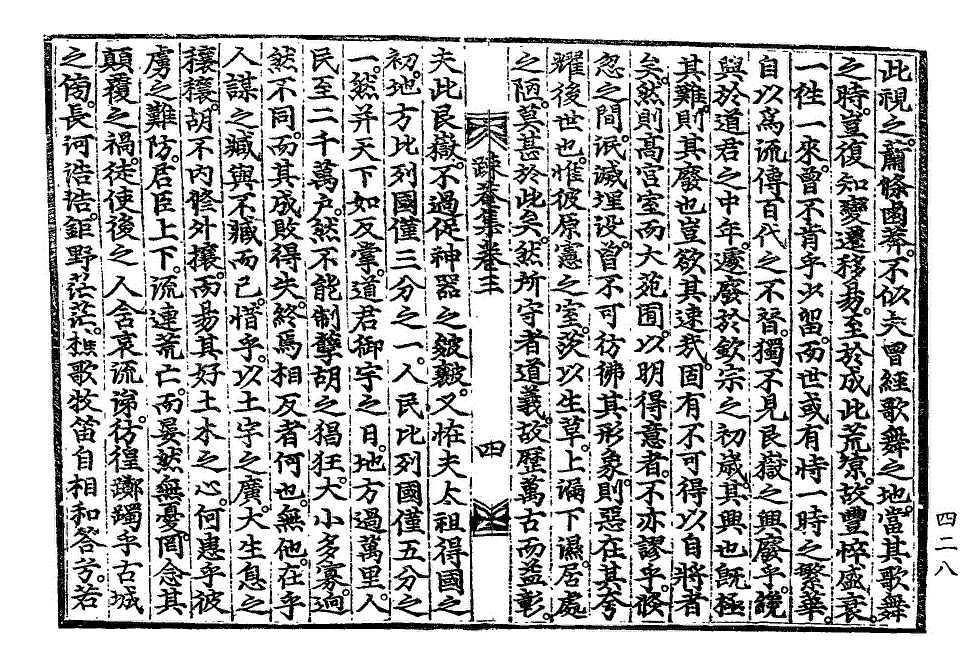 此视之。萧条卤莽。不似夫曾经歌舞之地。当其歌舞之时。岂复知变迁移易。至于成此荒凉。故丰悴盛衰。一往一来。曾不肯乎少留。而世或有恃一时之繁华。自以为流传百代之不替。独不见艮岳之兴废乎。才兴于道君之中年。遽废于钦宗之初岁。其兴也既极其难。则其废也岂欲其速哉。固有不可得以自将者矣。然则高宫室而大苑囿。以明得意者。不亦谬乎。倏忽之间。泯灭埋没。曾不可彷佛其形象。则恶在其夸耀后世也。惟彼原宪之室。茨以生草。上漏下湿。居处之陋。莫甚于此矣。然所守者道义。故历万古而益彰。夫此艮岳。不过促神器之皴𥀶。又怪夫太祖得国之初。地方比列国仅三分之一。人民比列国仅五分之一。然并天下如反掌。道君御宇之日。地方过万里。人民至二千万户。然不能制孽胡之猖狂。大小多寡。迥然不同。而其成败得失。终焉相反者何也。无他。在乎人谋之臧与不臧而已。惜乎。以土宇之广。大生息之穰穰。胡不内修外攘。而易其好土木之心。何患乎彼虏之难防。君臣上下。流连荒亡。而晏然无忧。罔念其颠覆之祸。徒使后之人含哀流涕。彷徨踯躅乎古城之傍。长河浩浩。钜野茫茫。樵歌牧笛自相和答兮。若
此视之。萧条卤莽。不似夫曾经歌舞之地。当其歌舞之时。岂复知变迁移易。至于成此荒凉。故丰悴盛衰。一往一来。曾不肯乎少留。而世或有恃一时之繁华。自以为流传百代之不替。独不见艮岳之兴废乎。才兴于道君之中年。遽废于钦宗之初岁。其兴也既极其难。则其废也岂欲其速哉。固有不可得以自将者矣。然则高宫室而大苑囿。以明得意者。不亦谬乎。倏忽之间。泯灭埋没。曾不可彷佛其形象。则恶在其夸耀后世也。惟彼原宪之室。茨以生草。上漏下湿。居处之陋。莫甚于此矣。然所守者道义。故历万古而益彰。夫此艮岳。不过促神器之皴𥀶。又怪夫太祖得国之初。地方比列国仅三分之一。人民比列国仅五分之一。然并天下如反掌。道君御宇之日。地方过万里。人民至二千万户。然不能制孽胡之猖狂。大小多寡。迥然不同。而其成败得失。终焉相反者何也。无他。在乎人谋之臧与不臧而已。惜乎。以土宇之广。大生息之穰穰。胡不内修外攘。而易其好土木之心。何患乎彼虏之难防。君臣上下。流连荒亡。而晏然无忧。罔念其颠覆之祸。徒使后之人含哀流涕。彷徨踯躅乎古城之傍。长河浩浩。钜野茫茫。樵歌牧笛自相和答兮。若疏庵先生集卷之三 第 4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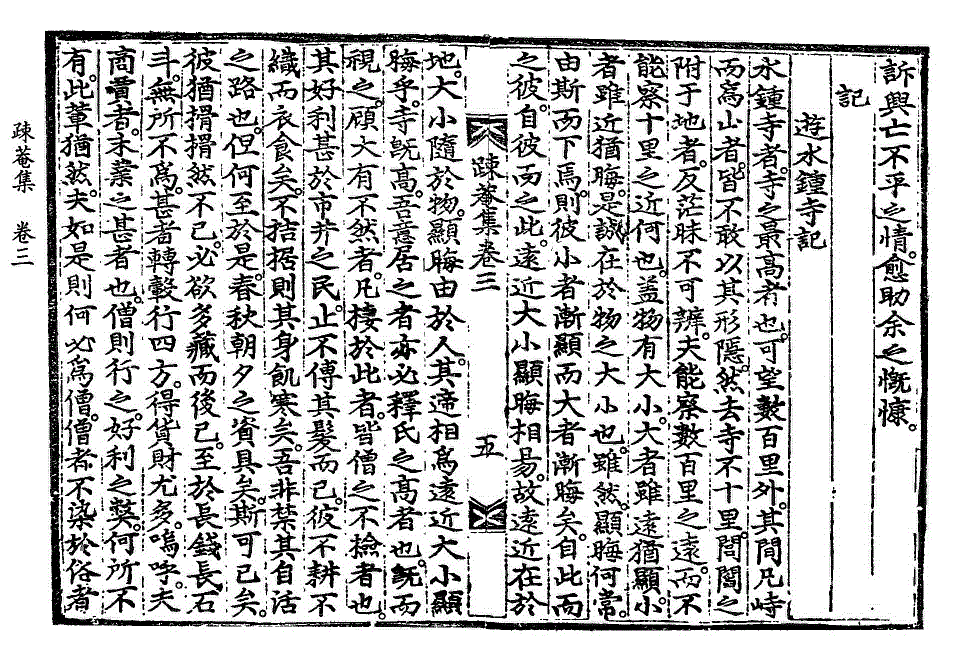 诉兴亡不平之情。愈助余之慨慷。
诉兴亡不平之情。愈助余之慨慷。疏庵先生集卷之三
记
游水钟寺记
水钟寺者。寺之最高者也。可望数百里外。其间兄峙而为山者。皆不敢以其形隐。然去寺不十里。闾阎之附于地者。反茫昧不可辨。夫能察数百里之远。而不能察十里之近何也。盖物有大小。大者虽远犹显。小者虽近犹晦。是诚在于物之大小也。虽然。显晦何常。由斯而下焉。则彼小者渐显而大者渐晦矣。自此而之彼。自彼而之此。远近大小显晦相易。故远近在于地。大小随于物。显晦由于人。其递相为远近大小显晦乎。寺既高。吾意居之者亦必释氏之高者也。既而视之。顾大有不然者。凡栖于此者。皆僧之不检者也。其好利甚于市井之民。止不传其发而已。彼不耕不织而衣食矣。不拮据则其身饥寒矣。吾非禁其自活之路也。但何至于是。春秋朝夕之资具矣。斯可已矣。彼犹搰搰然不已。必欲多藏而后已。至于长钱长石斗。无所不为。甚者转毂行四方。得货财尤多。呜呼。夫商贾者。禾业之甚者也。僧则行之。好利之弊。何所不有。此辈犹然。夫如是则何必为僧。僧者不染于俗者
疏庵先生集卷之三 第 429L 页
 也。此辈名则僧。实则俗。不亦滥乎。托其名于僧而徇其实于俗。以为僧也则非其实矣。以为俗也则非其名矣。此辈果何人哉。是不以僧之道自处。而欲人之待之以僧也。是不以俗之累自去。而恶人之呼之以俗也。误矣。此辈何不去释而复归于人。即父子君臣夫妇之道可复矣。夫舍父子君臣夫妇之道。深入山林。其终也止于斯焉。则归斯可矣。与其拥虚名而自陷于异端。不若归而复为人。以全父子君臣夫妇之道也。假令此辈得同行于佛。亦不贤于父子君臣夫妇之道矣。是日。适有供佛者。奉饮食置于佛前。若饭若饼若茶若果若菜之类。不可胜数。彼诚致力于此矣。虽然。是黩矣非礼也。何者。夫事神。不可不以礼。饮食之数。先王既有定制。不可违也。违之非礼矣。故圆丘,方泽,宗庙,社稷。祭之大者也。其笾豆亦不过十二。是岂不足于物哉。而止于此者。盖礼不可无节。无节则黩。黩则非礼。非所以事神者也。今佛亦神也。而事之不以礼。饮食之无节。至于如此。是黩矣非礼也。且其所以供佛之意。不过为死者祈福而已。福可祈而得耶。死者可祈而得。则生者亦可祈而得矣。然吾未见其祈而得者也。且祈于佛尤非也。佛苟可以福人。
也。此辈名则僧。实则俗。不亦滥乎。托其名于僧而徇其实于俗。以为僧也则非其实矣。以为俗也则非其名矣。此辈果何人哉。是不以僧之道自处。而欲人之待之以僧也。是不以俗之累自去。而恶人之呼之以俗也。误矣。此辈何不去释而复归于人。即父子君臣夫妇之道可复矣。夫舍父子君臣夫妇之道。深入山林。其终也止于斯焉。则归斯可矣。与其拥虚名而自陷于异端。不若归而复为人。以全父子君臣夫妇之道也。假令此辈得同行于佛。亦不贤于父子君臣夫妇之道矣。是日。适有供佛者。奉饮食置于佛前。若饭若饼若茶若果若菜之类。不可胜数。彼诚致力于此矣。虽然。是黩矣非礼也。何者。夫事神。不可不以礼。饮食之数。先王既有定制。不可违也。违之非礼矣。故圆丘,方泽,宗庙,社稷。祭之大者也。其笾豆亦不过十二。是岂不足于物哉。而止于此者。盖礼不可无节。无节则黩。黩则非礼。非所以事神者也。今佛亦神也。而事之不以礼。饮食之无节。至于如此。是黩矣非礼也。且其所以供佛之意。不过为死者祈福而已。福可祈而得耶。死者可祈而得。则生者亦可祈而得矣。然吾未见其祈而得者也。且祈于佛尤非也。佛苟可以福人。疏庵先生集卷之三 第 4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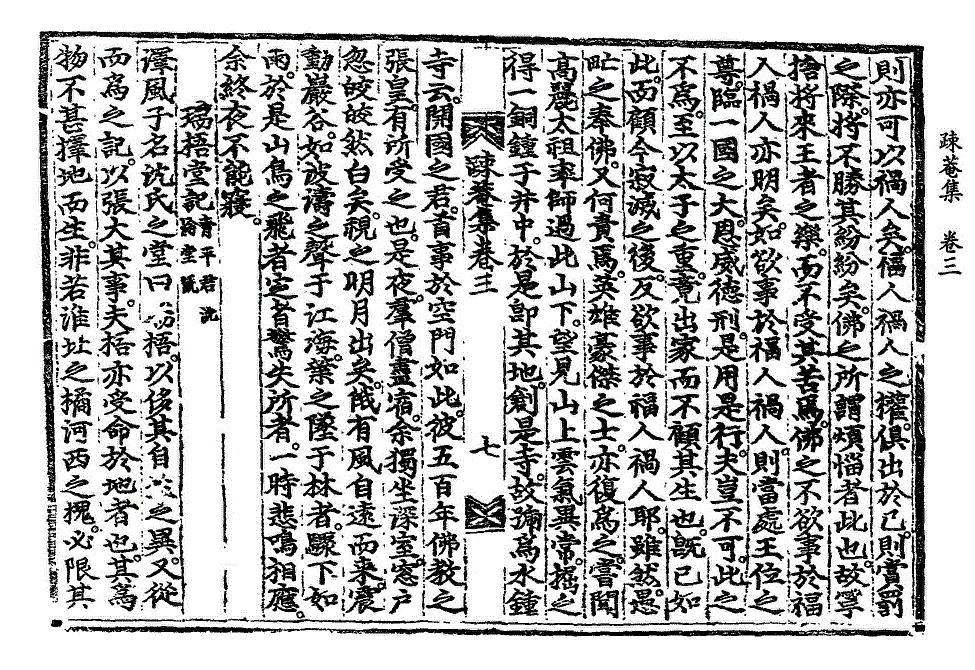 则亦可以祸人矣。福人祸人之权。俱出于己。则赏罚之际。将不胜其纷纷矣。佛之所谓烦恼者此也。故宁舍将来王者之乐。而不受其苦焉。佛之不欲事于福人祸人亦明矣。如欲事于福人祸人。则当处王位之尊。临一国之大。恩威德刑。是用是行。夫岂不可。此之不为。至以太子之重。竟出家而不顾其生也。既已如此。而顾今寂灭之后。反欲事于福人祸人耶。虽然。愚氓之奉佛。又何责焉。英雄豪杰之士。亦复为之。尝闻高丽太祖率师过此山下。望见山上云气异常。掘之得一铜钟于井中。于是即其地。创是寺。故号为水钟寺云。开国之君。首事于空门如此。彼五百年佛教之张皇。有所受之也。是夜。群僧尽宿。余独坐深室。窗户忽皎皎然白矣。视之明月出矣。俄有风自远而来。震动岩谷。如波涛之声于江海。叶之坠于林者。骤下如雨。于是山鸟之飞者定者惊失所者。一时悲鸣相应。余终夜不能寝。
则亦可以祸人矣。福人祸人之权。俱出于己。则赏罚之际。将不胜其纷纷矣。佛之所谓烦恼者此也。故宁舍将来王者之乐。而不受其苦焉。佛之不欲事于福人祸人亦明矣。如欲事于福人祸人。则当处王位之尊。临一国之大。恩威德刑。是用是行。夫岂不可。此之不为。至以太子之重。竟出家而不顾其生也。既已如此。而顾今寂灭之后。反欲事于福人祸人耶。虽然。愚氓之奉佛。又何责焉。英雄豪杰之士。亦复为之。尝闻高丽太祖率师过此山下。望见山上云气异常。掘之得一铜钟于井中。于是即其地。创是寺。故号为水钟寺云。开国之君。首事于空门如此。彼五百年佛教之张皇。有所受之也。是夜。群僧尽宿。余独坐深室。窗户忽皎皎然白矣。视之明月出矣。俄有风自远而来。震动岩谷。如波涛之声于江海。叶之坠于林者。骤下如雨。于是山鸟之飞者定者惊失所者。一时悲鸣相应。余终夜不能寝。瑞梧堂记(青平君沈惀堂号)
泽风子名沈氏之堂曰瑞梧。以侈其自然之异。又从而为之记。以张大其事。夫梧亦受命于地者也。其为物不甚择地而生。非若淮北之橘河西之槐。必限其
疏庵先生集卷之三 第 4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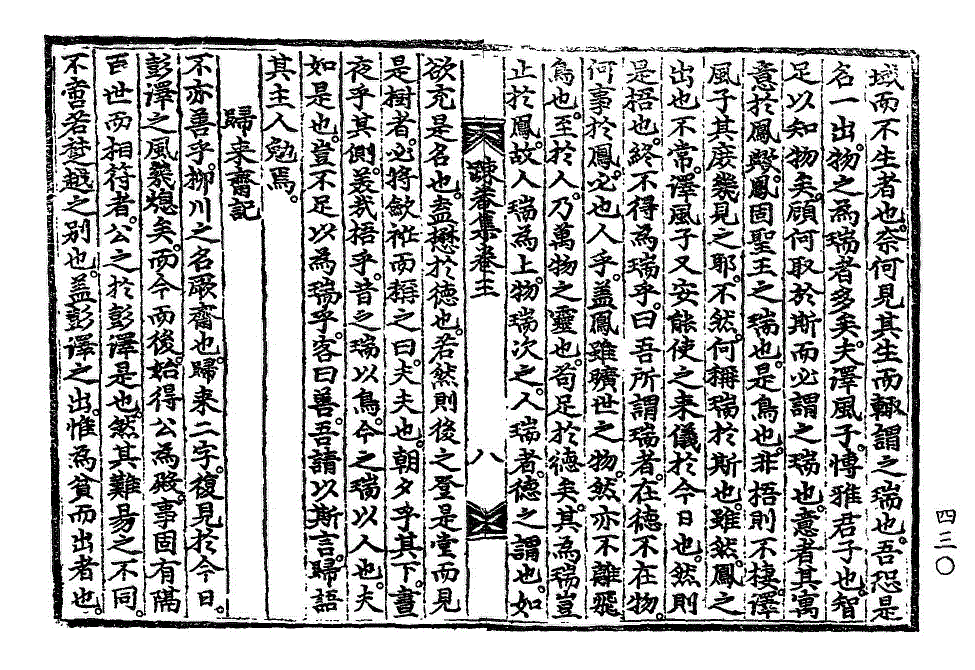 域而不生者也。奈何见其生而辄谓之瑞也。吾恐是名一出。物之为瑞者多矣。夫泽风子。博雅君子也。智足以知物矣。顾何取于斯而必谓之瑞也。意者其寓意于凤欤。凤固圣王之瑞也。是鸟也。非梧则不栖。泽风子其庶几见之耶。不然。何称瑞于斯也。虽然。凤之出也不常。泽风子又安能使之来仪于今日也。然则是梧也。终不得为瑞乎。曰吾所谓瑞者。在德不在物。何事于凤。必也人乎。盖凤虽旷世之物。然亦不离飞鸟也。至于人。乃万物之灵也。苟足于德矣。其为瑞岂止于凤。故人瑞为上。物瑞次之。人瑞者。德之谓也。如欲充是名也。盍懋于德也。若然则后之登是堂而见是树者。必将敛衽而称之曰。夫夫也。朝夕乎其下。昼夜乎其侧。美哉梧乎。昔之瑞以鸟。今之瑞以人也。夫如是也。岂不足以为瑞乎。客曰善。吾请以斯言。归语其主人勉焉。
域而不生者也。奈何见其生而辄谓之瑞也。吾恐是名一出。物之为瑞者多矣。夫泽风子。博雅君子也。智足以知物矣。顾何取于斯而必谓之瑞也。意者其寓意于凤欤。凤固圣王之瑞也。是鸟也。非梧则不栖。泽风子其庶几见之耶。不然。何称瑞于斯也。虽然。凤之出也不常。泽风子又安能使之来仪于今日也。然则是梧也。终不得为瑞乎。曰吾所谓瑞者。在德不在物。何事于凤。必也人乎。盖凤虽旷世之物。然亦不离飞鸟也。至于人。乃万物之灵也。苟足于德矣。其为瑞岂止于凤。故人瑞为上。物瑞次之。人瑞者。德之谓也。如欲充是名也。盍懋于德也。若然则后之登是堂而见是树者。必将敛衽而称之曰。夫夫也。朝夕乎其下。昼夜乎其侧。美哉梧乎。昔之瑞以鸟。今之瑞以人也。夫如是也。岂不足以为瑞乎。客曰善。吾请以斯言。归语其主人勉焉。归来斋记
不亦善乎。柳川之名厥斋也。归来二字。复见于今日。彭泽之风几熄矣。而今而后。始得公为殿。事固有隔百世而相符者。公之于彭泽是也。然其难易之不同。不啻若楚越之别也。盖彭泽之出。惟为贫而出者也。
疏庵先生集卷之三 第 4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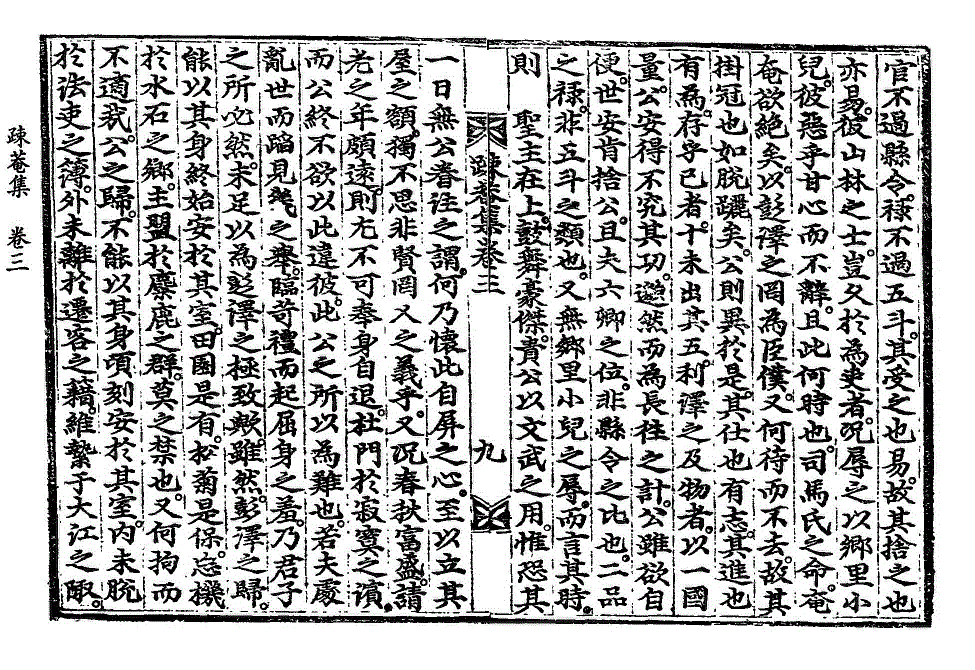 官不过县令。禄不过五斗。其受之也易。故其舍之也亦易。彼山林之士。岂久于为吏者。况辱之以乡里小儿。彼恶乎甘心而不辞。且此何时也。司马氏之命。奄奄欲绝矣。以彭泽之罔为臣仆。又何待而不去。故其挂冠也如脱躧矣。公则异于是。其仕也有志。其进也有为。存乎己者。十未出其五。利泽之及物者。以一国量。公安得不究其功。邈然而为长往之计。公虽欲自便。世安肯舍公。且夫六卿之位。非县令之比也。二品之禄。非五斗之类也。又无乡里小儿之辱。而言其时。则 圣主在上。鼓舞豪杰。贵公以文武之用。惟恐其一日无公眷注之谓。何乃怀此自屏之心。至以立其屋之额。独不思非贤罔又之义乎。又况春秋富盛。请老之年颇远。则尤不可奉身自退。杜门于寂寞之滨。而公终不欲以此违彼。此公之所以为难也。若夫处乱世而蹈见几之举。临苛礼而起屈身之羞。乃君子之所必然。未足以为彭泽之极致欤。虽然。彭泽之归。能以其身终始安于其室。田园是有。松菊是保。忘机于水石之乡。主盟于麋鹿之群。莫之禁也。又何拘而不适哉。公之归。不能以其身顷刻安于其室。内未脱于法吏之簿。外未离于迁客之籍。维絷于大江之陬。
官不过县令。禄不过五斗。其受之也易。故其舍之也亦易。彼山林之士。岂久于为吏者。况辱之以乡里小儿。彼恶乎甘心而不辞。且此何时也。司马氏之命。奄奄欲绝矣。以彭泽之罔为臣仆。又何待而不去。故其挂冠也如脱躧矣。公则异于是。其仕也有志。其进也有为。存乎己者。十未出其五。利泽之及物者。以一国量。公安得不究其功。邈然而为长往之计。公虽欲自便。世安肯舍公。且夫六卿之位。非县令之比也。二品之禄。非五斗之类也。又无乡里小儿之辱。而言其时。则 圣主在上。鼓舞豪杰。贵公以文武之用。惟恐其一日无公眷注之谓。何乃怀此自屏之心。至以立其屋之额。独不思非贤罔又之义乎。又况春秋富盛。请老之年颇远。则尤不可奉身自退。杜门于寂寞之滨。而公终不欲以此违彼。此公之所以为难也。若夫处乱世而蹈见几之举。临苛礼而起屈身之羞。乃君子之所必然。未足以为彭泽之极致欤。虽然。彭泽之归。能以其身终始安于其室。田园是有。松菊是保。忘机于水石之乡。主盟于麋鹿之群。莫之禁也。又何拘而不适哉。公之归。不能以其身顷刻安于其室。内未脱于法吏之簿。外未离于迁客之籍。维絷于大江之陬。疏庵先生集卷之三 第 4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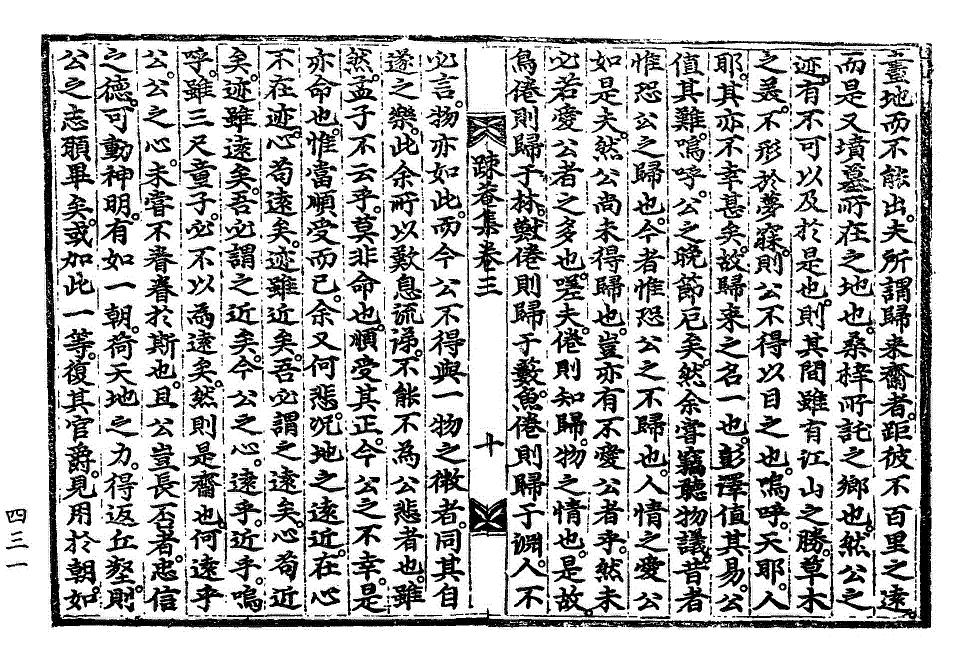 画地而不能出。夫所谓归来斋者。距彼不百里之远。而是又坟墓所在之地也。桑梓所托之乡也。然公之迹。有不可以及于是也。则其间虽有江山之胜。草木之美。不形于梦寐。则公不得以目之也。呜呼。天耶。人耶。其亦不幸甚矣。故归来之名一也。彭泽值其易。公值其难。呜呼。公之晚节厄矣。然余尝窃听物议。昔者惟恐公之归也。今者惟恐公之不归也。人情之爱公如是夫。然公尚未得归也。岂亦有不爱公者乎。然未必若爱公者之多也。嗟夫。倦则知归。物之情也。是故。鸟倦则归于林。兽倦则归于薮。鱼倦则归于渊。人不必言。物亦如此。而今公不得与一物之微者。同其自遂之乐。此余所以叹息流涕。不能不为公悲者也。虽然。孟子不云乎。莫非命也。顺受其正。今公之不幸。是亦命也。惟当顺受而已。余又何悲。况地之远近。在心不在迹。心苟远矣。迹虽近矣。吾必谓之远矣。心苟近矣。迹虽远矣。吾必谓之近矣。今公之心。远乎。近乎。呜呼。虽三尺童子。必不以为远矣。然则是斋也。何远乎公。公之心。未尝不眷眷于斯也。且公岂长否者。忠信之德。可动神明。有如一朝。荷天地之力。得返丘壑。则公之志愿毕矣。或加此一等。复其官爵。见用于朝。如
画地而不能出。夫所谓归来斋者。距彼不百里之远。而是又坟墓所在之地也。桑梓所托之乡也。然公之迹。有不可以及于是也。则其间虽有江山之胜。草木之美。不形于梦寐。则公不得以目之也。呜呼。天耶。人耶。其亦不幸甚矣。故归来之名一也。彭泽值其易。公值其难。呜呼。公之晚节厄矣。然余尝窃听物议。昔者惟恐公之归也。今者惟恐公之不归也。人情之爱公如是夫。然公尚未得归也。岂亦有不爱公者乎。然未必若爱公者之多也。嗟夫。倦则知归。物之情也。是故。鸟倦则归于林。兽倦则归于薮。鱼倦则归于渊。人不必言。物亦如此。而今公不得与一物之微者。同其自遂之乐。此余所以叹息流涕。不能不为公悲者也。虽然。孟子不云乎。莫非命也。顺受其正。今公之不幸。是亦命也。惟当顺受而已。余又何悲。况地之远近。在心不在迹。心苟远矣。迹虽近矣。吾必谓之远矣。心苟近矣。迹虽远矣。吾必谓之近矣。今公之心。远乎。近乎。呜呼。虽三尺童子。必不以为远矣。然则是斋也。何远乎公。公之心。未尝不眷眷于斯也。且公岂长否者。忠信之德。可动神明。有如一朝。荷天地之力。得返丘壑。则公之志愿毕矣。或加此一等。复其官爵。见用于朝。如疏庵先生集卷之三 第 4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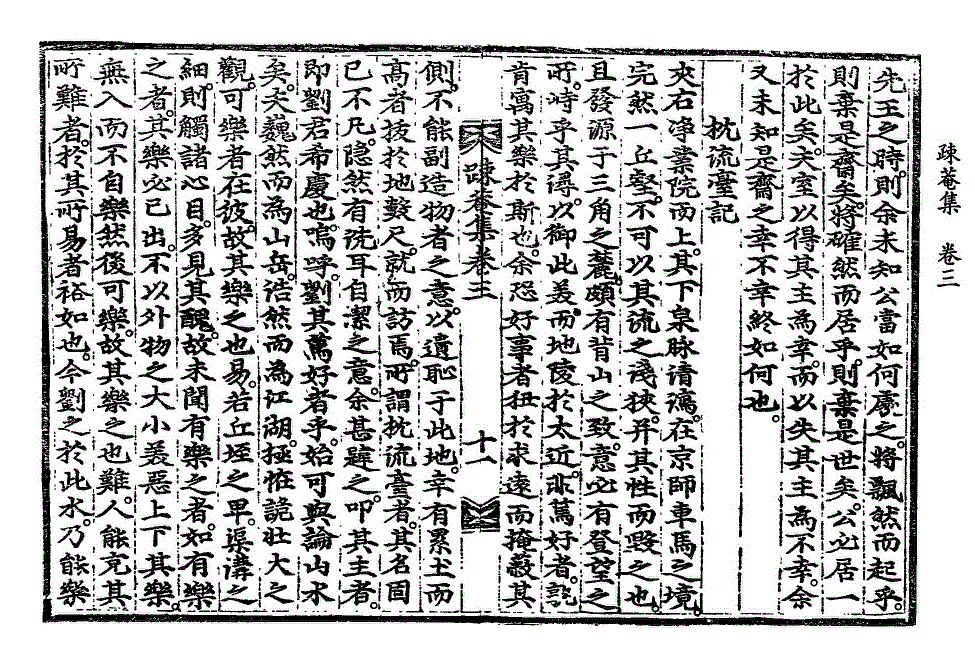 先王之时。则余未知公当如何处之。将飘然而起乎。则弃是斋矣。将确然而居乎。则弃是世矣。公必居一于此矣。夫室以得其主为幸。而以失其主为不幸。余又未知是斋之幸不幸终如何也。
先王之时。则余未知公当如何处之。将飘然而起乎。则弃是斋矣。将确然而居乎。则弃是世矣。公必居一于此矣。夫室以得其主为幸。而以失其主为不幸。余又未知是斋之幸不幸终如何也。枕流台记
夹右净业院而上。其下泉脉清泻。在京师车马之境。完然一丘壑。不可以其流之浅狭。并其性而毁之也。且发源于三角之麓。颇有背山之致。意必有登望之所。峙乎其浔。以御此美。而地陵于太近。非笃好者。孰肯寓其乐于斯也。余恐好事者狃于求远而掩蔽其侧。不能副造物者之意。以遗耻于此地。幸有累土而高者拔于地数尺。就而访焉。所谓枕流台者。其名固已不凡。隐然有洗耳自洁之意。余甚韪之。叩其主者。即刘君希庆也。呜呼。刘其笃好者乎。始可与论山水矣。夫巍然而为山岳。浩然而为江湖。极怪诡壮大之观。可乐者在彼。故其乐之也易。若丘垤之卑。渠沟之细。则触诸心目。多见其丑。故未闻有乐之者。如有乐之者。其乐必已出。不以外物之大小美恶上下其乐。无入而不自乐然后可乐。故其乐之也难。人能克其所难者。于其所易者裕如也。今刘之于此水。乃能乐
疏庵先生集卷之三 第 4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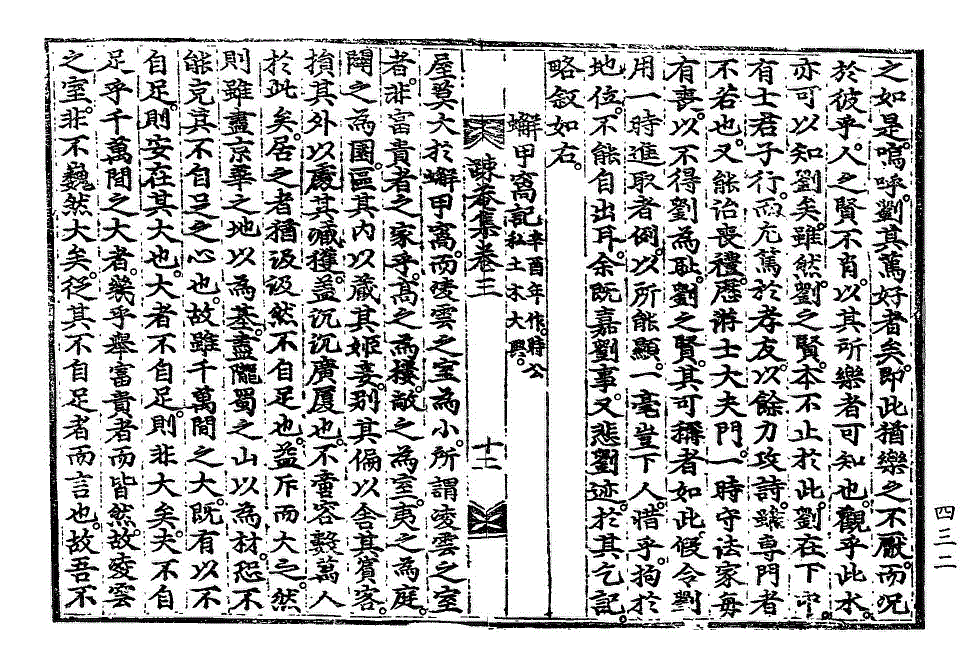 之如是。呜呼。刘其笃好者矣。即此犹乐之不厌。而况于彼乎。人之贤不肖。以其所乐者可知也。观乎此水。亦可以知刘矣。虽然。刘之贤。本不止于此。刘在下中。有士君子行。而尤笃于孝友。以馀力攻诗。虽专门者不若也。又能治丧礼。历游士大夫门。一时守法家每有丧。以不得刘为耻。刘之贤。其可称者如此。假令刘用一时进取者例。以所能显。一毫岂下人。惜乎。拘于地位。不能自出耳。余既嘉刘事。又悲刘迹。于其乞记。略叙如右。
之如是。呜呼。刘其笃好者矣。即此犹乐之不厌。而况于彼乎。人之贤不肖。以其所乐者可知也。观乎此水。亦可以知刘矣。虽然。刘之贤。本不止于此。刘在下中。有士君子行。而尤笃于孝友。以馀力攻诗。虽专门者不若也。又能治丧礼。历游士大夫门。一时守法家每有丧。以不得刘为耻。刘之贤。其可称者如此。假令刘用一时进取者例。以所能显。一毫岂下人。惜乎。拘于地位。不能自出耳。余既嘉刘事。又悲刘迹。于其乞记。略叙如右。蟹甲窝记(辛酉年作。时公私土木大兴。)
屋莫大于蟹甲窝。而凌云之室为小。所谓凌云之室者。非富贵者之家乎。高之为楼。敞之为室。夷之为庭。辟之为园。区其内以藏其姬妾。别其偏以舍其宾客。损其外以处其臧获。盖沈沈广厦也。不啻容数万人于此矣。居之者犹汲汲然不自足也。益斥而大之。然则虽尽京华之地以为基。尽陇蜀之山以为材。恐不能克其不自足之心也。故虽千万间之大。既有以不自足。则安在其大也。大者不自足。则非大矣。夫不自足乎千万间之大者。几乎举富贵者而皆然。故凌云之室。非不巍然大矣。从其不自足者而言也。故吾不
疏庵先生集卷之三 第 433H 页
 曰大而曰小也。至如蟹甲窝。乃屋之黍累者也。既谓之蟹甲。则其小也似不满一指也。居之者犹坦坦然自足也。大于此者。虽得志不为也。则其所以自足者信然矣。故虽一指之小。既有以自足。则安在其小也。小者自足乎自足。则非小矣。夫自足乎一指之小者。犹不乏其人也。故蟹甲窝。非不眇然以小矣。从其自足者而言也。故吾不曰小而曰大也。大抵天下之物。无大无小。足于人者。虽小亦大。不足于人者。虽大亦小。今夫蟹甲窝。屋之至小者也。凌云之室。屋之至大者也。然蟹甲窝足于人。而凌云之室不足于人。吾故曰屋莫大于蟹甲窝而凌云之室为小也。且子独不闻蜗角之左右。有蛮触二国乎。物之小者。莫甚于此矣。然能容二国于此。今蟹甲之小。不至如蜗角。一家之大。不至如二国。而蜗之上。犹能容二国。则蟹甲之内。独不能容一家乎。则蟹甲比蜗角又大也。且虽居蟹甲窝之苦。不犹愈于鱼腹之葬乎。昔者屈原放逐江潭。卜居而不能决。其终也。投汨罗而死。葬其骨于鱼腹之中。今子亦放逐之臣也。蟹甲亦鱼腹之类也。然屈原葬之以死。子居之以生。子之幸顾不多也欤。奚暇言蟹甲窝之小哉。子其卧于斯起于斯。寝食于
曰大而曰小也。至如蟹甲窝。乃屋之黍累者也。既谓之蟹甲。则其小也似不满一指也。居之者犹坦坦然自足也。大于此者。虽得志不为也。则其所以自足者信然矣。故虽一指之小。既有以自足。则安在其小也。小者自足乎自足。则非小矣。夫自足乎一指之小者。犹不乏其人也。故蟹甲窝。非不眇然以小矣。从其自足者而言也。故吾不曰小而曰大也。大抵天下之物。无大无小。足于人者。虽小亦大。不足于人者。虽大亦小。今夫蟹甲窝。屋之至小者也。凌云之室。屋之至大者也。然蟹甲窝足于人。而凌云之室不足于人。吾故曰屋莫大于蟹甲窝而凌云之室为小也。且子独不闻蜗角之左右。有蛮触二国乎。物之小者。莫甚于此矣。然能容二国于此。今蟹甲之小。不至如蜗角。一家之大。不至如二国。而蜗之上。犹能容二国。则蟹甲之内。独不能容一家乎。则蟹甲比蜗角又大也。且虽居蟹甲窝之苦。不犹愈于鱼腹之葬乎。昔者屈原放逐江潭。卜居而不能决。其终也。投汨罗而死。葬其骨于鱼腹之中。今子亦放逐之臣也。蟹甲亦鱼腹之类也。然屈原葬之以死。子居之以生。子之幸顾不多也欤。奚暇言蟹甲窝之小哉。子其卧于斯起于斯。寝食于疏庵先生集卷之三 第 4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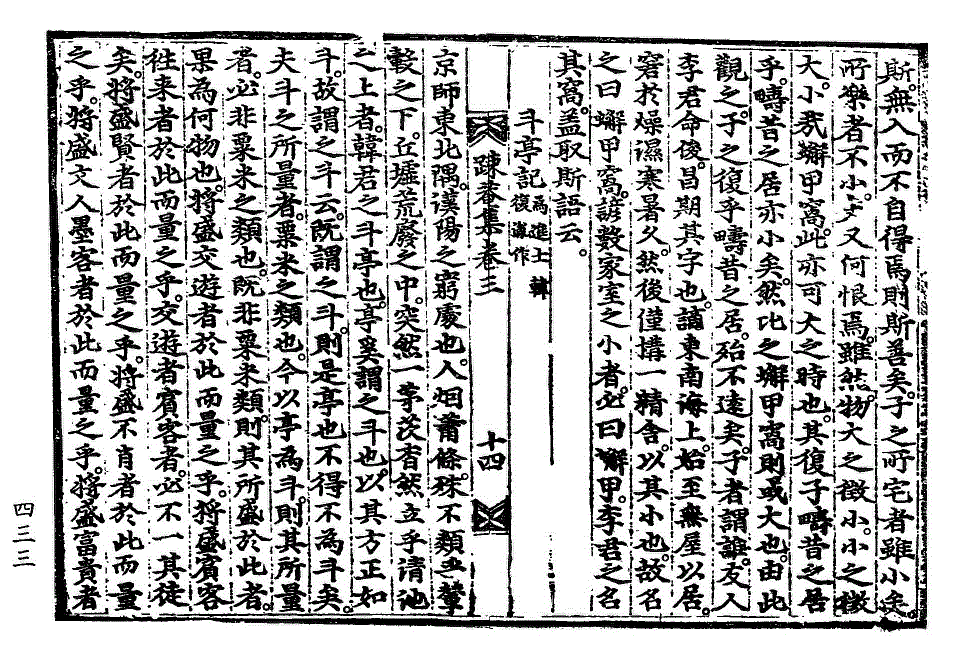 斯。无入而不自得焉则斯善矣。子之所宅者虽小矣。所乐者不小矣。又何恨焉。虽然。物大之徵小。小之徵大。小哉蟹甲窝。此亦可大之时也。其复子畴昔之居乎。畴昔之居亦小矣。然比之蟹甲窝则或大也。由此观之。子之复乎畴昔之居。殆不远矣。子者谓谁。友人李君命俊。昌期其字也。谪东南海上。始至无屋以居。窘于燥灦寒暑久。然后仅构一精舍。以其小也。故名之曰蟹甲窝。谚数家室之小者。必曰蟹甲。李君之名其窝。盖取斯语云。
斯。无入而不自得焉则斯善矣。子之所宅者虽小矣。所乐者不小矣。又何恨焉。虽然。物大之徵小。小之徵大。小哉蟹甲窝。此亦可大之时也。其复子畴昔之居乎。畴昔之居亦小矣。然比之蟹甲窝则或大也。由此观之。子之复乎畴昔之居。殆不远矣。子者谓谁。友人李君命俊。昌期其字也。谪东南海上。始至无屋以居。窘于燥灦寒暑久。然后仅构一精舍。以其小也。故名之曰蟹甲窝。谚数家室之小者。必曰蟹甲。李君之名其窝。盖取斯语云。斗亭记(为进士韩复浦作)
京师东北隅。汉阳之穷处也。人烟萧条。殊不类乎辇毂之下。丘墟荒废之中。突然一茅茨杳然立乎清池之上者。韩君之斗亭也。亭奚谓之斗也。以其方正如斗。故谓之斗云。既谓之斗。则是亭也不得不为斗矣。夫斗之所量者。粟米之类也。今以亭为斗。则其所量者。必非粟米之类也。既非粟米类。则其所盛于此者。果为何物也。将盛交游者于此而量之乎。将盛宾客往来者于此而量之乎。交游者宾客者。必不一其徒矣。将盛贤者于此而量之乎。将盛不肖者于此而量之乎。将盛文人墨客者于此而量之乎。将盛富贵者
疏庵先生集卷之三 第 434H 页
 于此而量之乎。将盛贫贱者于此而量之乎。五者之中。亦不一其人矣。有循儒之嫡者焉。有学墨之僻者焉。有动遵法式者焉。有挟筴读书。探索幽赜者焉。有博古知今。无所不覈者焉。有武夫之不可束者焉。有勇士之不可触者焉。有俊杰超卓。蕴雄谋硕画者焉。有规规于功名之倜倜者焉。有公卿大夫巍巍赫赫者焉。有下僚百执事官位不陟者焉。有老成之肃肃者焉。有年少之仆仆者焉。有学问不息者焉。有饥寒不能毒者焉。有祸福不能易者焉。有难进易退。不污其迹者焉。有专攻屈,宋,李,杜之绳墨程度。以为绩者焉。有炫耀才华。扬扬自得者焉。有干禄者焉。有隐君子而韫匮者焉。有耿介不忒者焉。有疏通阔达。不为畛域者焉。有磊落俶傥。不脩边幅者焉。有思深虑逖者焉。有乐天知命。超然自适者焉。有责之以仁辅之以德者焉。有孝友之笃者焉。有节义之勖者焉。有公正而自剋者焉。有谨慎而自敕者焉。有温恭和穆者焉。有刚毅正直者焉。有慈良而不酷者焉。有辞让而不渎者焉。有廉耻自饬者焉。有以礼自检。惟己之克者焉。有孤立独行。不倚势力者焉。有慷慨奋激者焉。有果敢而不可扼者焉。有顽钝而无所识者焉。有猖
于此而量之乎。将盛贫贱者于此而量之乎。五者之中。亦不一其人矣。有循儒之嫡者焉。有学墨之僻者焉。有动遵法式者焉。有挟筴读书。探索幽赜者焉。有博古知今。无所不覈者焉。有武夫之不可束者焉。有勇士之不可触者焉。有俊杰超卓。蕴雄谋硕画者焉。有规规于功名之倜倜者焉。有公卿大夫巍巍赫赫者焉。有下僚百执事官位不陟者焉。有老成之肃肃者焉。有年少之仆仆者焉。有学问不息者焉。有饥寒不能毒者焉。有祸福不能易者焉。有难进易退。不污其迹者焉。有专攻屈,宋,李,杜之绳墨程度。以为绩者焉。有炫耀才华。扬扬自得者焉。有干禄者焉。有隐君子而韫匮者焉。有耿介不忒者焉。有疏通阔达。不为畛域者焉。有磊落俶傥。不脩边幅者焉。有思深虑逖者焉。有乐天知命。超然自适者焉。有责之以仁辅之以德者焉。有孝友之笃者焉。有节义之勖者焉。有公正而自剋者焉。有谨慎而自敕者焉。有温恭和穆者焉。有刚毅正直者焉。有慈良而不酷者焉。有辞让而不渎者焉。有廉耻自饬者焉。有以礼自检。惟己之克者焉。有孤立独行。不倚势力者焉。有慷慨奋激者焉。有果敢而不可扼者焉。有顽钝而无所识者焉。有猖疏庵先生集卷之三 第 4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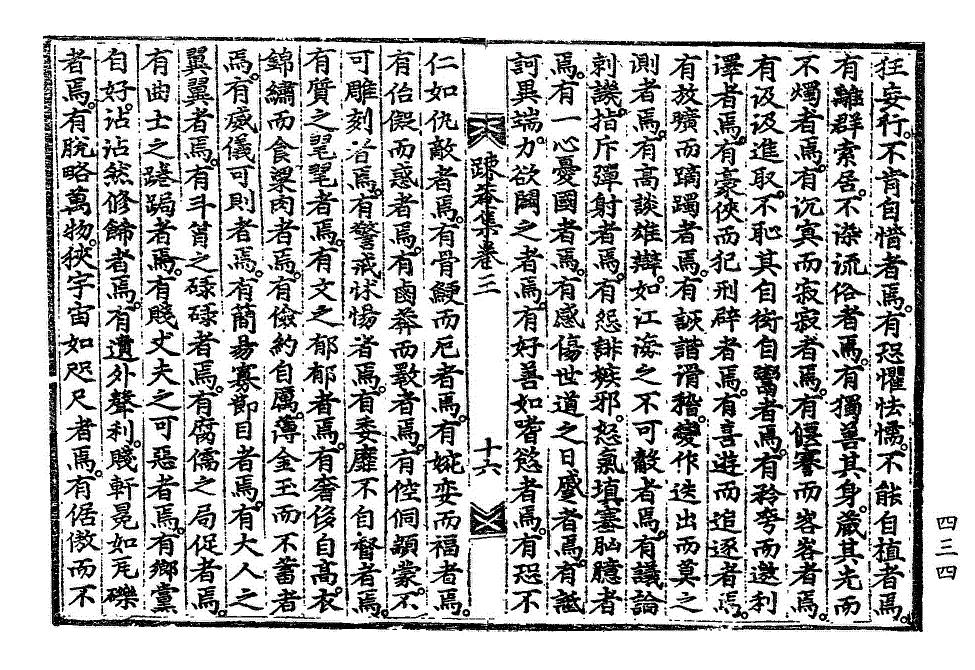 狂妄行。不肯自惜者焉。有恐惧怯懦。不能自植者焉。有离群索居。不染流俗者焉。有独善其身。藏其光而不烛者焉。有沈冥而寂寂者焉。有偃謇而峉峉者焉。有汲汲进取。不耻其自衒自鬻者焉。有矜夸而邀利泽者焉。有豪侠而犯刑辟者焉。有喜游而追逐者焉。有放旷而蹢躅者焉。有诙谐滑稽。变作迭出而莫之测者焉。有高谈雄辩。如江海之不可觳者焉。有议论刺讥。指斥弹射者焉。有怨诽嫉邪。怒气填塞脑臆者焉。有一心忧国者焉。有感伤世道之日蹙者焉。有诋诃异端。力欲辟之者焉。有好善如嗜欲者焉。有恐不仁如仇敌者焉。有骨鲠而厄者焉。有婉奕而福者焉。有佁儗而惑者焉。有卤莽而斁者焉。有倥侗颛蒙。不可雕刻者焉。有警戒怵惕者焉。有委靡不自督者焉。有质之毣毣者焉。有文之郁郁者焉。有奢侈自高。衣锦绣而食粱肉者焉。有俭约自厉。薄金玉而不蓄者焉。有威仪可则者焉。有简易寡节目者焉。有大人之翼翼者焉。有斗筲之碌碌者焉。有腐儒之局促者焉。有曲士之蜷跼者焉。有贱丈夫之可恶者焉。有乡党自好。沾沾然修饰者焉。有遗外声利。贱轩冕如瓦砾者焉。有脱略万物。狭宇宙如咫尺者焉。有倨傲而不
狂妄行。不肯自惜者焉。有恐惧怯懦。不能自植者焉。有离群索居。不染流俗者焉。有独善其身。藏其光而不烛者焉。有沈冥而寂寂者焉。有偃謇而峉峉者焉。有汲汲进取。不耻其自衒自鬻者焉。有矜夸而邀利泽者焉。有豪侠而犯刑辟者焉。有喜游而追逐者焉。有放旷而蹢躅者焉。有诙谐滑稽。变作迭出而莫之测者焉。有高谈雄辩。如江海之不可觳者焉。有议论刺讥。指斥弹射者焉。有怨诽嫉邪。怒气填塞脑臆者焉。有一心忧国者焉。有感伤世道之日蹙者焉。有诋诃异端。力欲辟之者焉。有好善如嗜欲者焉。有恐不仁如仇敌者焉。有骨鲠而厄者焉。有婉奕而福者焉。有佁儗而惑者焉。有卤莽而斁者焉。有倥侗颛蒙。不可雕刻者焉。有警戒怵惕者焉。有委靡不自督者焉。有质之毣毣者焉。有文之郁郁者焉。有奢侈自高。衣锦绣而食粱肉者焉。有俭约自厉。薄金玉而不蓄者焉。有威仪可则者焉。有简易寡节目者焉。有大人之翼翼者焉。有斗筲之碌碌者焉。有腐儒之局促者焉。有曲士之蜷跼者焉。有贱丈夫之可恶者焉。有乡党自好。沾沾然修饰者焉。有遗外声利。贱轩冕如瓦砾者焉。有脱略万物。狭宇宙如咫尺者焉。有倨傲而不疏庵先生集卷之三 第 4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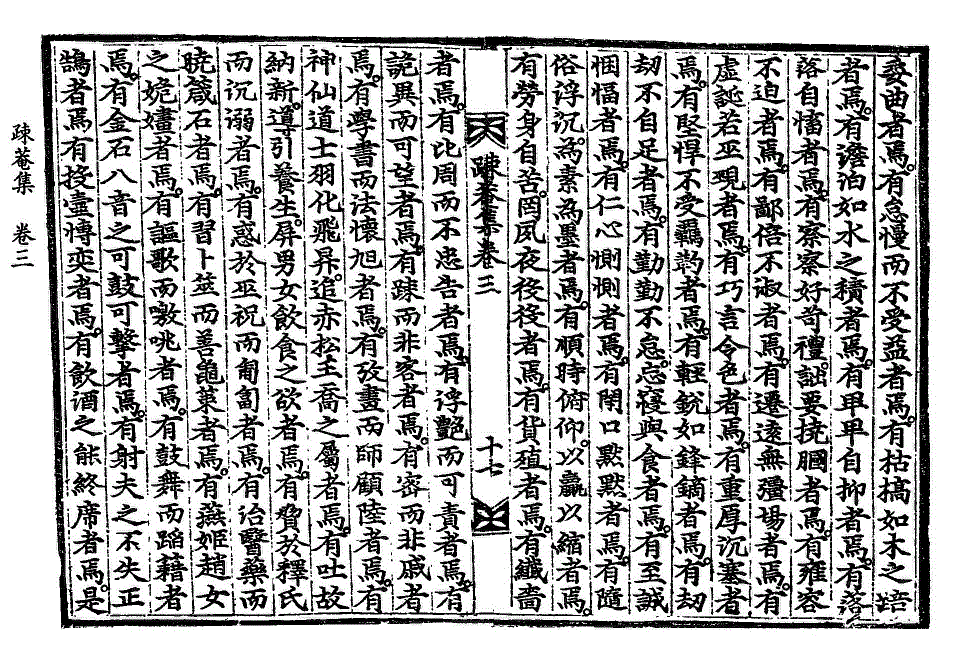 委曲者焉。有怠慢而不受益者焉。有枯槁如木之踣者焉。有澹泊如水之积者焉。有卑卑自抑者焉。有落落自慉者焉。有察察好苛礼。诎要挠腘者焉。有雍容不迫者焉。有鄙倍不淑者焉。有迁远无疆场者焉。有虚诞若巫觋者焉。有巧言令色者焉。有重厚沈塞者焉。有坚悍不受羁靮者焉。有轻锐如锋镝者焉。有劫劫不自足者焉。有勤勤不怠。忘寝与食者焉。有至诚悃愊者焉。有仁心恻恻者焉。有闭口默默者焉。有随俗浮沈。为素为墨者焉。有顺时俯仰。以赢以缩者焉。有劳身自苦。罔夙夜役役者焉。有货殖者焉。有纤啬者焉。有比周而不忠告者焉。有浮艳而可责者焉。有诡异而可望者焉。有疏而非客者焉。有密而非戚者焉。有学书而法怀旭者焉。有考画而师顾陆者焉。有神仙道士羽化飞升。追赤松王乔之属者焉。有吐故纳新。导引养生。屏男女饮食之欲者焉。有胁于释氏而沈溺者焉。有惑于巫祝而匍匐者焉。有治医药而晓箴石者焉。有习卜筮而善龟策者焉。有燕姬赵女之姽婳者焉。有讴歌而噭咷者焉。有鼓舞而蹈籍者焉。有金石八音之可鼓可击者焉。有射夫之不失正鹄者焉。有投壶博奕者焉。有饮酒之能终席者焉。是
委曲者焉。有怠慢而不受益者焉。有枯槁如木之踣者焉。有澹泊如水之积者焉。有卑卑自抑者焉。有落落自慉者焉。有察察好苛礼。诎要挠腘者焉。有雍容不迫者焉。有鄙倍不淑者焉。有迁远无疆场者焉。有虚诞若巫觋者焉。有巧言令色者焉。有重厚沈塞者焉。有坚悍不受羁靮者焉。有轻锐如锋镝者焉。有劫劫不自足者焉。有勤勤不怠。忘寝与食者焉。有至诚悃愊者焉。有仁心恻恻者焉。有闭口默默者焉。有随俗浮沈。为素为墨者焉。有顺时俯仰。以赢以缩者焉。有劳身自苦。罔夙夜役役者焉。有货殖者焉。有纤啬者焉。有比周而不忠告者焉。有浮艳而可责者焉。有诡异而可望者焉。有疏而非客者焉。有密而非戚者焉。有学书而法怀旭者焉。有考画而师顾陆者焉。有神仙道士羽化飞升。追赤松王乔之属者焉。有吐故纳新。导引养生。屏男女饮食之欲者焉。有胁于释氏而沈溺者焉。有惑于巫祝而匍匐者焉。有治医药而晓箴石者焉。有习卜筮而善龟策者焉。有燕姬赵女之姽婳者焉。有讴歌而噭咷者焉。有鼓舞而蹈籍者焉。有金石八音之可鼓可击者焉。有射夫之不失正鹄者焉。有投壶博奕者焉。有饮酒之能终席者焉。是疏庵先生集卷之三 第 4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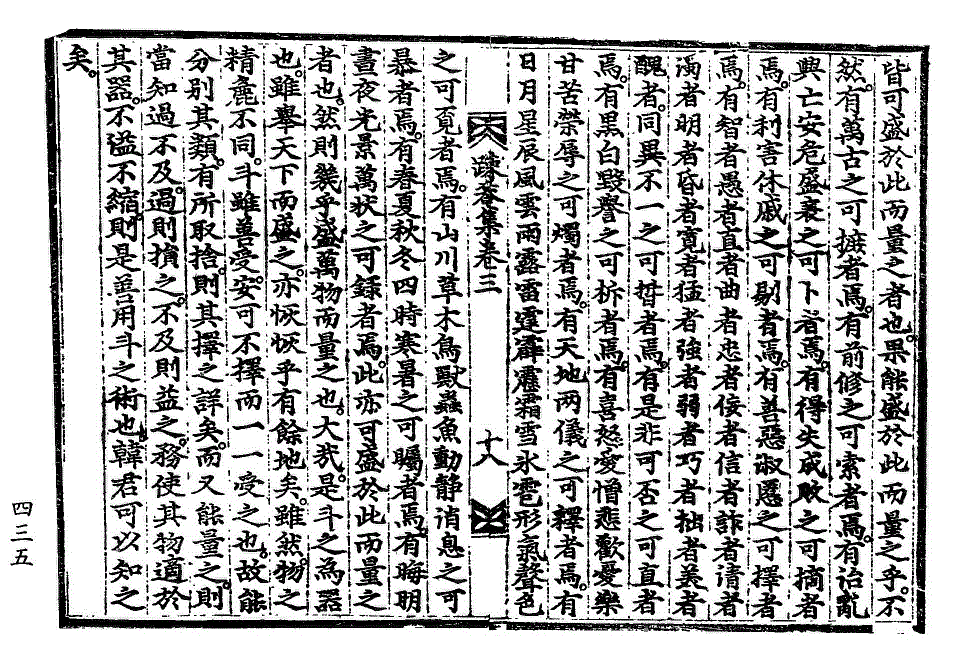 皆可盛于此而量之者也。果能盛于此而量之乎。不然。有万古之可摭者焉。有前修之可索者焉。有治乱兴亡安危盛衰之可卜者焉。有得失成败之可摘者焉。有利害休戚之可剔者焉。有善恶淑慝之可择者焉。有智者愚者直者曲者忠者佞者信者诈者清者浊者明者昏者宽者猛者强者弱者巧者拙者美者丑者。同异不一之可晢者焉。有是非可否之可直者焉。有黑白毁誉之可柝者焉。有喜怒爱憎悲欢忧乐甘苦荣辱之可烛者焉。有天地两仪之可释者焉。有日月星辰风云雨露雷霆霹雳霜雪冰雹形气声色之可觅者焉。有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动静消息之可暴者焉。有春夏秋冬四时寒暑之可瞩者焉。有晦明昼夜光景万状之可录者焉。此亦可盛于此而量之者也。然则几乎盛万物而量之也。大哉。是斗之为器也。虽举天下而盛之。亦恢恢乎有馀地矣。虽然。物之精粗不同。斗虽善受。安可不择而一一受之也。故能分别其类。有所取舍。则其择之详矣。而又能量之。则当知过不及。过则损之。不及则益之。务使其物适于其器。不溢不缩。则是善用斗之术也。韩君可以知之矣。
皆可盛于此而量之者也。果能盛于此而量之乎。不然。有万古之可摭者焉。有前修之可索者焉。有治乱兴亡安危盛衰之可卜者焉。有得失成败之可摘者焉。有利害休戚之可剔者焉。有善恶淑慝之可择者焉。有智者愚者直者曲者忠者佞者信者诈者清者浊者明者昏者宽者猛者强者弱者巧者拙者美者丑者。同异不一之可晢者焉。有是非可否之可直者焉。有黑白毁誉之可柝者焉。有喜怒爱憎悲欢忧乐甘苦荣辱之可烛者焉。有天地两仪之可释者焉。有日月星辰风云雨露雷霆霹雳霜雪冰雹形气声色之可觅者焉。有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动静消息之可暴者焉。有春夏秋冬四时寒暑之可瞩者焉。有晦明昼夜光景万状之可录者焉。此亦可盛于此而量之者也。然则几乎盛万物而量之也。大哉。是斗之为器也。虽举天下而盛之。亦恢恢乎有馀地矣。虽然。物之精粗不同。斗虽善受。安可不择而一一受之也。故能分别其类。有所取舍。则其择之详矣。而又能量之。则当知过不及。过则损之。不及则益之。务使其物适于其器。不溢不缩。则是善用斗之术也。韩君可以知之矣。疏庵先生集卷之三 第 4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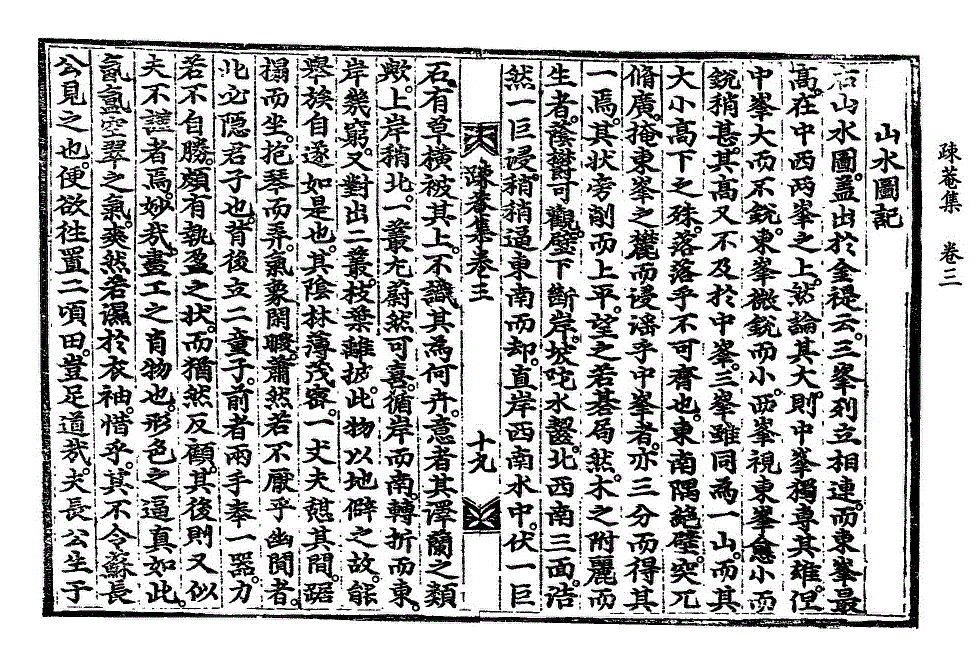 山水图记
山水图记右山水图。盖出于金禔云。三峰列立相连。而东峰最高。在中西两峰之上。然论其大。则中峰独专其雄。但中峰大而不锐。东峰微锐而小。西峰视东峰愈小而锐稍甚。其高又不及于中峰。三峰虽同为一山。而其大小高下之殊。落落乎不可齐也。东南隅绝壁。突兀脩广。掩东峰之麓而浸淫乎中峰者。亦三分而得其一焉。其状旁削而上平。望之若棋局然。木之附丽而生者。荫郁可观。壁下断岸。坡咤水齧。北西南三面。浩然一巨浸。稍稍逼东南而却。直岸西南水中。伏一巨石。有草横被其上。不识其为何卉。意者其泽兰之类欤。上岸稍北。一丛尤蔚然可喜。循岸而南。转折而东。岸几穷。又对出二丛。枝叶离披。此物以地僻之故。能举族自遂如是也。其阴林薄茂密。一丈夫憩其间。踞榻而坐。抱琴而弄。气象闲暇。萧然若不厌乎幽阒者。北必隐君子也。背后立二童子。前者两手奉一器。力若不自胜。颇有执盈之状。而犹然反顾。其后则又似夫不谨者焉。妙哉。画工之肖物也。形色之逼真如此。氤氲空翠之气。爽然若湿于衣袖。惜乎。其不令苏长公见之也。便欲往置二顷田。岂足道哉。夫长公生于
疏庵先生集卷之三 第 436L 页
 西蜀。仕于京师。历抵于秦陇齐赵江淮楚越之郊。席不暇暖。当此之时。举天下之大而无一亩之可耕。乃欲置二顷田于画中之境。不亦过乎。余则异于是。但欲一探其胜。不敢望二顷田于其中。必不得已而为诛茅之计。则依岩石傍林木。眇然立一环堵。其广足以容膝。即止日采竹实松子及薇蕨之属食之。渴则饮溪涧之水。此外余复何求。彼长公之志。过矣过矣。嗟呼。余安得此境而有之。余固乐而忘忧。枕烟霞而席丘壑。夫焉有所厌。虽然。余之观山水亦多矣。搜幽剔深。往往得胜绝之处。余未尝栖迟于其侧。而顾独眷眷于画图。不几于叶公之好龙乎。天下之遗其真而取其似者。若是乎其不少矣。余安敢不自警于斯画。
西蜀。仕于京师。历抵于秦陇齐赵江淮楚越之郊。席不暇暖。当此之时。举天下之大而无一亩之可耕。乃欲置二顷田于画中之境。不亦过乎。余则异于是。但欲一探其胜。不敢望二顷田于其中。必不得已而为诛茅之计。则依岩石傍林木。眇然立一环堵。其广足以容膝。即止日采竹实松子及薇蕨之属食之。渴则饮溪涧之水。此外余复何求。彼长公之志。过矣过矣。嗟呼。余安得此境而有之。余固乐而忘忧。枕烟霞而席丘壑。夫焉有所厌。虽然。余之观山水亦多矣。搜幽剔深。往往得胜绝之处。余未尝栖迟于其侧。而顾独眷眷于画图。不几于叶公之好龙乎。天下之遗其真而取其似者。若是乎其不少矣。余安敢不自警于斯画。归休堂记(为李公培元作)
已矣乎。吾未见归休者也。位于朝者。或杜门习静。非公事不出。是几乎休矣。而然谓之归则不可。退于野者。或悒悒然热中。终夜不能寝。是几乎归矣。而然谓之休则不可。故能归而不能自休。则非所以为归矣。能休而不能自归。则非所以为休矣。其惟养伯之归休乎。归焉而不失其所以休。休焉而不违其所以归
疏庵先生集卷之三 第 4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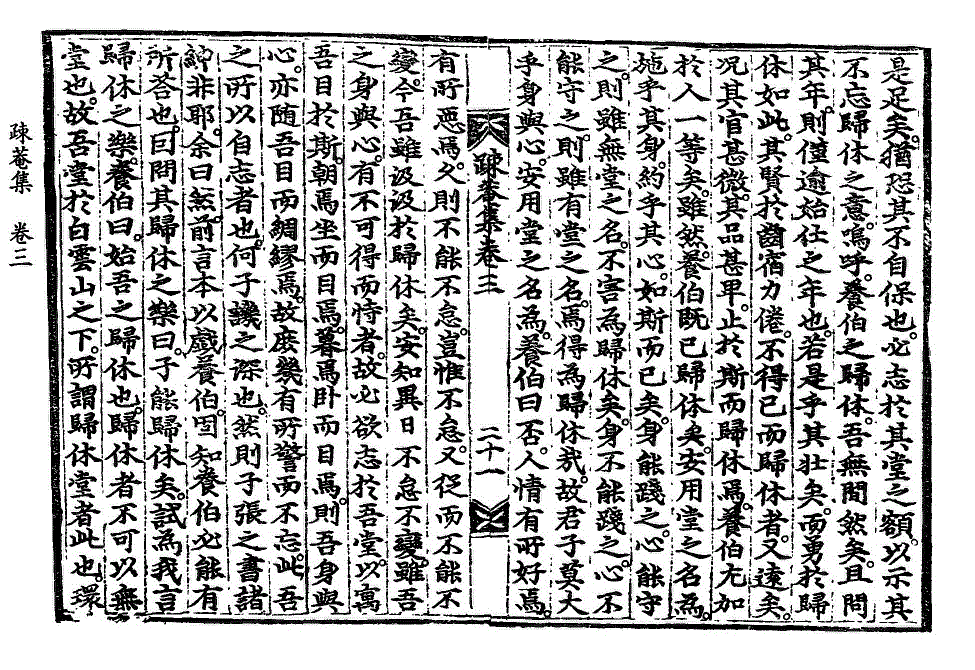 是足矣。犹恐其不自保也。必志于其堂之额。以示其不忘归休之意。呜呼。养伯之归休。吾无间然矣。且问其年。则仅逾始仕之年也。若是乎其壮矣。而勇于归休如此。其贤于齿宿力倦。不得已而归休者。又远矣。况其官甚微。其品甚卑。止于斯而归休焉。养伯尤加于人一等矣。虽然。养伯既已归休矣。安用堂之名为。施乎其身。约乎其心。如斯而已矣。身能践之。心能守之。则虽无堂之名。不害为归休矣。身不能践之。心不能守之。则虽有堂之名。焉得为归休哉。故君子莫大乎身与心。安用堂之名为。养伯曰否。人情有所好焉。有所恶焉。久则不能不怠。岂惟不怠。又从而不能不变。今吾虽汲汲于归休矣。安知异日不怠不变。虽吾之身与心。有不可得而恃者。故必欲志于吾堂。以寓吾目于斯。朝焉坐而目焉。暮焉卧而目焉。则吾身与心。亦随吾目而绸缪焉。故庶几有所警而不忘。此吾之所以自志者也。何子讥之深也。然则子张之书诸绅非耶。余曰然。前言本以戏养伯。固知养伯必能有所答也。因问其归休之乐曰。子能归休矣。试为我言归休之乐。养伯曰。始吾之归休也。归休者不可以无堂也。故吾堂于白云山之下。所谓归休堂者此也。环
是足矣。犹恐其不自保也。必志于其堂之额。以示其不忘归休之意。呜呼。养伯之归休。吾无间然矣。且问其年。则仅逾始仕之年也。若是乎其壮矣。而勇于归休如此。其贤于齿宿力倦。不得已而归休者。又远矣。况其官甚微。其品甚卑。止于斯而归休焉。养伯尤加于人一等矣。虽然。养伯既已归休矣。安用堂之名为。施乎其身。约乎其心。如斯而已矣。身能践之。心能守之。则虽无堂之名。不害为归休矣。身不能践之。心不能守之。则虽有堂之名。焉得为归休哉。故君子莫大乎身与心。安用堂之名为。养伯曰否。人情有所好焉。有所恶焉。久则不能不怠。岂惟不怠。又从而不能不变。今吾虽汲汲于归休矣。安知异日不怠不变。虽吾之身与心。有不可得而恃者。故必欲志于吾堂。以寓吾目于斯。朝焉坐而目焉。暮焉卧而目焉。则吾身与心。亦随吾目而绸缪焉。故庶几有所警而不忘。此吾之所以自志者也。何子讥之深也。然则子张之书诸绅非耶。余曰然。前言本以戏养伯。固知养伯必能有所答也。因问其归休之乐曰。子能归休矣。试为我言归休之乐。养伯曰。始吾之归休也。归休者不可以无堂也。故吾堂于白云山之下。所谓归休堂者此也。环疏庵先生集卷之三 第 4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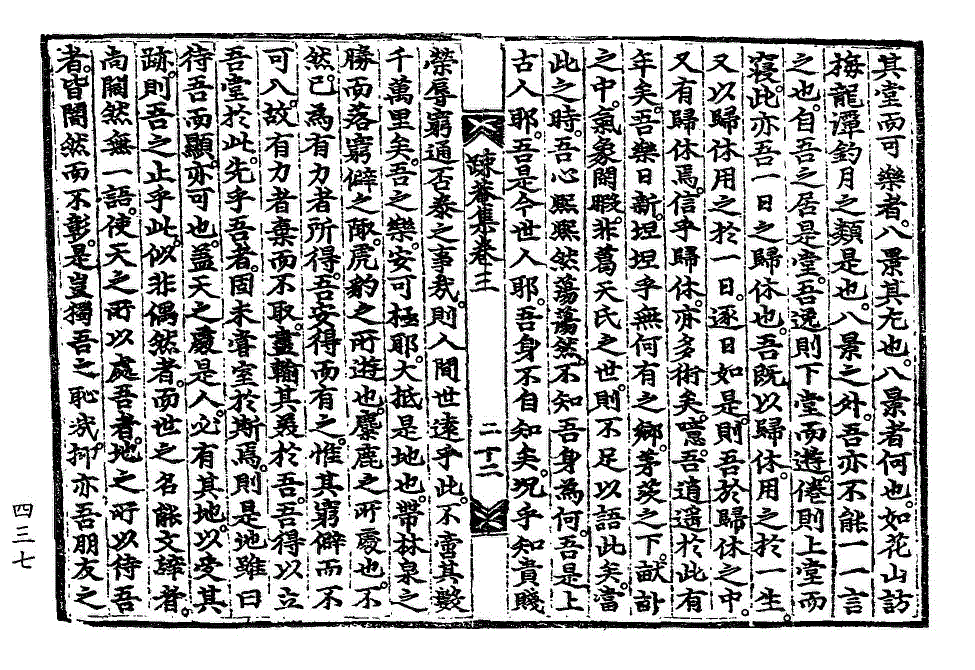 其堂而可乐者。八景其尤也。八景者何也。如花山访梅龙潭钓月之类是也。八景之外。吾亦不能一一言之也。自吾之居是堂。吾逸则下堂而游。倦则上堂而寝。此亦吾一日之归休也。吾既以归休。用之于一生。又以归休用之于一日。逐日如是。则吾于归休之中。又有归休焉。信乎归休。亦多术矣。噫。吾逍遥于此有年矣。吾乐日新。坦坦乎无何有之乡。茅茨之下。畎亩之中。气象闲暇。非葛天氏之世。则不足以语此矣。当此之时。吾心熙熙然荡荡然。不知吾身为何。吾是上古人耶。吾是今世人耶。吾身不自知矣。况乎知贵贱荣辱穷通否泰之事哉。则人间世远乎此。不啻其数千万里矣。吾之乐。安可极耶。大抵是地也。带林泉之胜而落穷僻之陬。虎豹之所游也。麋鹿之所处也。不然。已为有力者所得。吾安得而有之。惟其穷僻而不可入。故有力者弃而不取。尽输其美于吾。吾得以立吾堂于此。先乎吾者。固未尝室于斯焉。则是地虽曰待吾而显。亦可也。盖天之处是人。必有其地。以受其迹。则吾之止乎此。似非偶然者。而世之名能文辞者。尚阙然无一语。使天之所以处吾者。地之所以待吾者。皆闇然而不彰。是岂独吾之耻哉。抑亦吾朋友之
其堂而可乐者。八景其尤也。八景者何也。如花山访梅龙潭钓月之类是也。八景之外。吾亦不能一一言之也。自吾之居是堂。吾逸则下堂而游。倦则上堂而寝。此亦吾一日之归休也。吾既以归休。用之于一生。又以归休用之于一日。逐日如是。则吾于归休之中。又有归休焉。信乎归休。亦多术矣。噫。吾逍遥于此有年矣。吾乐日新。坦坦乎无何有之乡。茅茨之下。畎亩之中。气象闲暇。非葛天氏之世。则不足以语此矣。当此之时。吾心熙熙然荡荡然。不知吾身为何。吾是上古人耶。吾是今世人耶。吾身不自知矣。况乎知贵贱荣辱穷通否泰之事哉。则人间世远乎此。不啻其数千万里矣。吾之乐。安可极耶。大抵是地也。带林泉之胜而落穷僻之陬。虎豹之所游也。麋鹿之所处也。不然。已为有力者所得。吾安得而有之。惟其穷僻而不可入。故有力者弃而不取。尽输其美于吾。吾得以立吾堂于此。先乎吾者。固未尝室于斯焉。则是地虽曰待吾而显。亦可也。盖天之处是人。必有其地。以受其迹。则吾之止乎此。似非偶然者。而世之名能文辞者。尚阙然无一语。使天之所以处吾者。地之所以待吾者。皆闇然而不彰。是岂独吾之耻哉。抑亦吾朋友之疏庵先生集卷之三 第 4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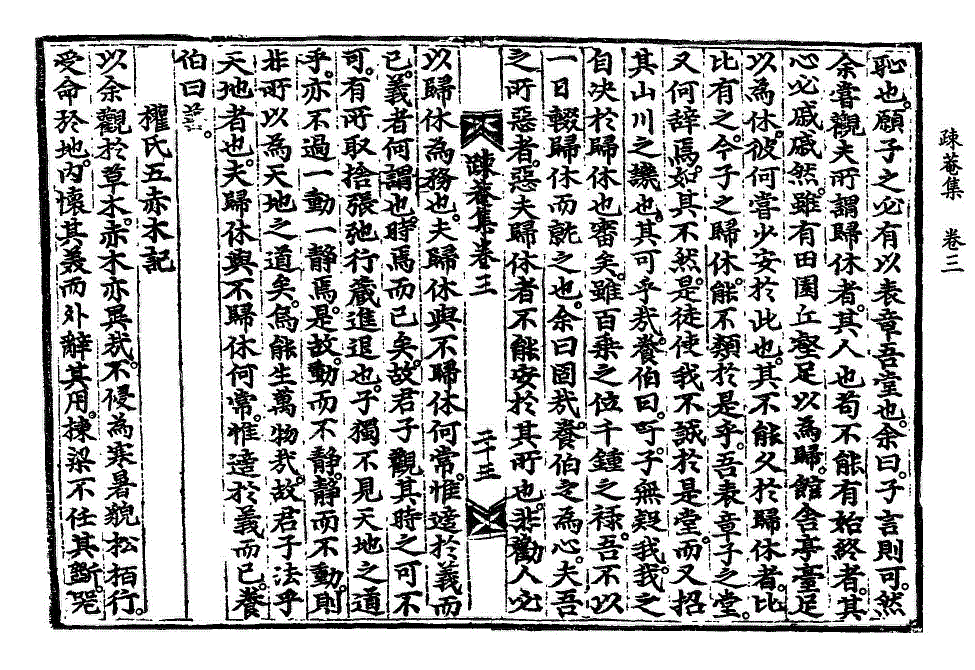 耻也。愿子之必有以表章吾堂也。余曰。子言则可。然余尝观夫所谓归休者。其人也苟不能有始终者。其心必戚戚然。虽有田园丘壑足以为归。馆舍亭台足以为休。彼何尝少安于此也。其不能久于归休者。比比有之。今子之归休。能不类于是乎。吾表章子之堂。又何辞焉。如其不然。是徒使我不诚于是堂。而又招其山川之讥也。其可乎哉。养伯曰。吁。子无疑我。我之自决于归休也审矣。虽百乘之位千钟之禄。吾不以一日辍归休而就之也。余曰固哉。养伯之为心。夫吾之所恶者。恶夫归休者不能安于其所也。非劝人必以归休为务也。夫归休与不归休何常。惟适于义而已。义者何谓也。时焉而已矣。故君子观其时之可不可。有所取舍张弛行藏进退也。子独不见天地之道乎。亦不过一动一静焉。是故。动而不静。静而不动。则非所以为天地之道矣。乌能生万物哉。故君子法乎天地者也。夫归休与不归休何常。惟适于义而已。养伯曰善。
耻也。愿子之必有以表章吾堂也。余曰。子言则可。然余尝观夫所谓归休者。其人也苟不能有始终者。其心必戚戚然。虽有田园丘壑足以为归。馆舍亭台足以为休。彼何尝少安于此也。其不能久于归休者。比比有之。今子之归休。能不类于是乎。吾表章子之堂。又何辞焉。如其不然。是徒使我不诚于是堂。而又招其山川之讥也。其可乎哉。养伯曰。吁。子无疑我。我之自决于归休也审矣。虽百乘之位千钟之禄。吾不以一日辍归休而就之也。余曰固哉。养伯之为心。夫吾之所恶者。恶夫归休者不能安于其所也。非劝人必以归休为务也。夫归休与不归休何常。惟适于义而已。义者何谓也。时焉而已矣。故君子观其时之可不可。有所取舍张弛行藏进退也。子独不见天地之道乎。亦不过一动一静焉。是故。动而不静。静而不动。则非所以为天地之道矣。乌能生万物哉。故君子法乎天地者也。夫归休与不归休何常。惟适于义而已。养伯曰善。权氏五赤木记
以余观于草木。赤木亦异哉。不侵为寒暑貌松柏行。受命于地。内怀其美而外辞其用。栋梁不任其斲。器
疏庵先生集卷之三 第 4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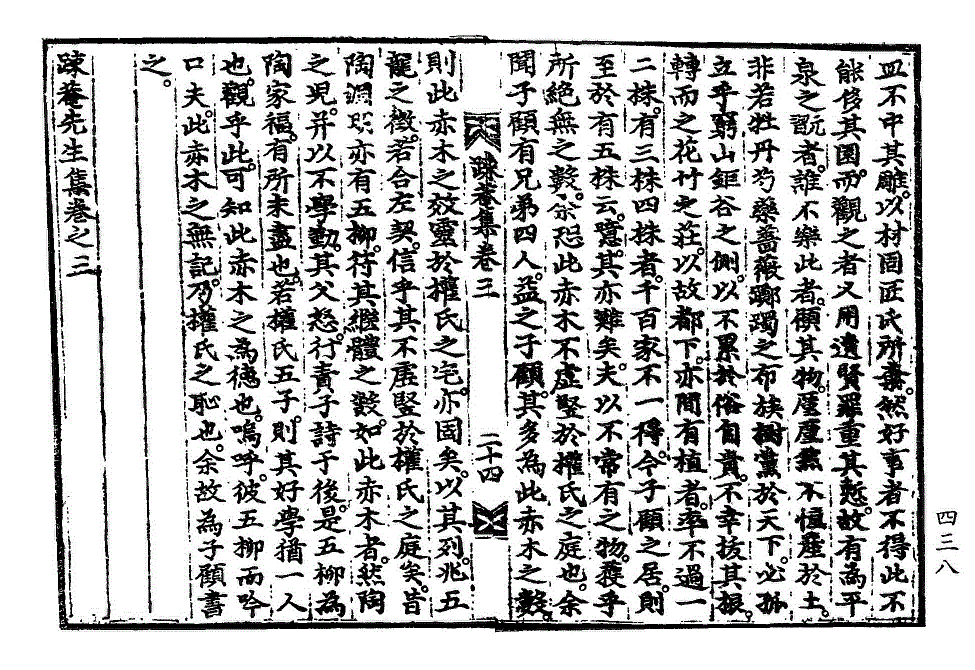 皿不中其雕。以村同匠氏所弃。然好事者不得此不能侈其园。而观之者又用遗贤罪重其惭。故有为平泉之玩者。谁不乐此者。顾其物。廑廑然不恒产于土。非若牡丹芍药蔷薇踯躅之布族树党于天下。必孤立乎穷山钜谷之侧。以不累于俗自贵。不幸拔其根。转而之花竹之庄。以故都下。亦间有植者。率不过一二株。有三株四株者。千百家不一得。今子顾之居。则至于有五株云。噫。其亦难矣。夫以不常有之物。获乎所绝无之数。余恐此赤木不虚竖于权氏之庭也。余闻子顾有兄弟四人。益之子顾。其多为此赤木之数。则此赤木之效灵于权氏之宅。亦固矣。以其列。兆五龙之徵。若合左契。信乎其不虚竖于权氏之庭矣。昔陶渊明亦有五柳。符其继体之数。如此赤木者。然陶之儿。并以不学勤。其父怒。行责子诗于后。是五柳为陶家福。有所未尽也。若权氏五子。则其好学犹一人也。观乎此。可知此赤木之为德也。呜呼。彼五柳而吟口夫。此赤木之无记。乃权氏之耻也。余故为子顾书之。
皿不中其雕。以村同匠氏所弃。然好事者不得此不能侈其园。而观之者又用遗贤罪重其惭。故有为平泉之玩者。谁不乐此者。顾其物。廑廑然不恒产于土。非若牡丹芍药蔷薇踯躅之布族树党于天下。必孤立乎穷山钜谷之侧。以不累于俗自贵。不幸拔其根。转而之花竹之庄。以故都下。亦间有植者。率不过一二株。有三株四株者。千百家不一得。今子顾之居。则至于有五株云。噫。其亦难矣。夫以不常有之物。获乎所绝无之数。余恐此赤木不虚竖于权氏之庭也。余闻子顾有兄弟四人。益之子顾。其多为此赤木之数。则此赤木之效灵于权氏之宅。亦固矣。以其列。兆五龙之徵。若合左契。信乎其不虚竖于权氏之庭矣。昔陶渊明亦有五柳。符其继体之数。如此赤木者。然陶之儿。并以不学勤。其父怒。行责子诗于后。是五柳为陶家福。有所未尽也。若权氏五子。则其好学犹一人也。观乎此。可知此赤木之为德也。呜呼。彼五柳而吟口夫。此赤木之无记。乃权氏之耻也。余故为子顾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