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x 页
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混定编录(续集)
混定编录(续集)
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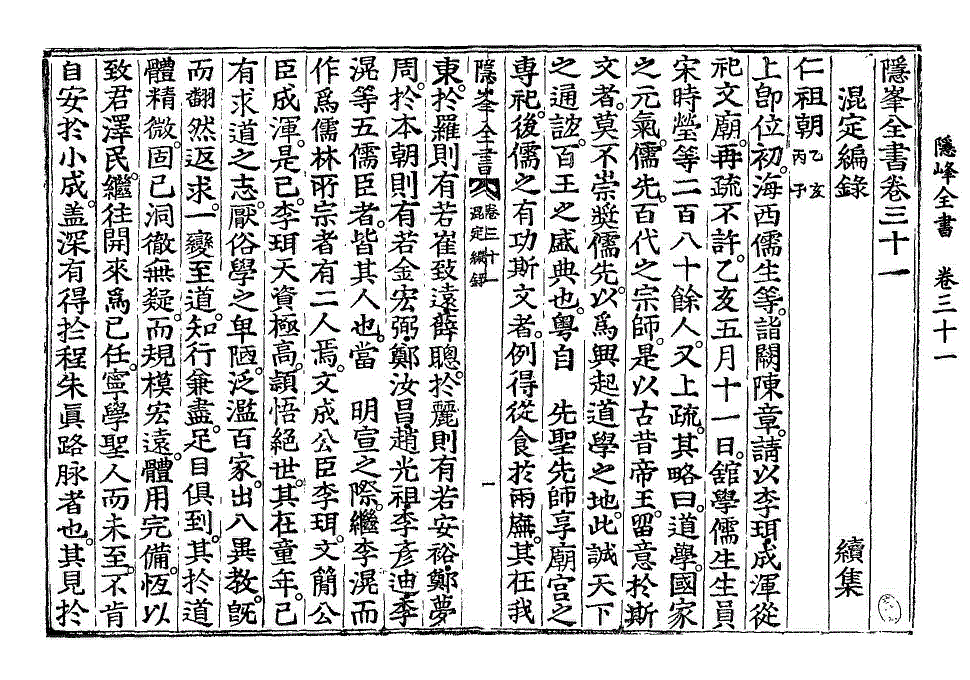 仁祖朝(乙亥丙子)
仁祖朝(乙亥丙子)上即位初。海西儒生等。诣阙陈章。请以李珥,成浑从祀文庙。再疏不许。乙亥五月十一日。馆学儒生生员宋时莹等二百八十馀人。又上疏。其略曰。道学。国家之元气。儒先。百代之宗师。是以古昔帝王。留意于斯文者。莫不崇奖儒先。以为兴起道学之地。此诚天下之通谊。百王之盛典也。粤自 先圣先师享庙宫之专祀。后儒之有功斯文者。例得从食于两庑。其在我东。于罗则有若崔致远,薛聪。于丽则有若安裕,郑梦周。于本朝则有若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李彦迪,季滉等五儒臣者。皆其人也。当 明宣之际。继李滉而作为儒林所宗者有二人焉。文成公臣李珥。文简公臣成浑。是已。李珥天资极高。颖悟绝世。其在童年。已有求道之志。厌俗学之卑陋。泛滥百家。出入异教。既而翻然返求。一变至道。知行兼尽。足目俱到。其于道体精微。固已洞彻无疑。而规模宏远。体用完备。恒以致君泽民。继往开来为己任。宁学圣人而未至。不肯自安于小成。盖深有得于程朱真路脉者也。其见于
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18L 页
 著述者击蒙要诀。极切于学者日用功程。而圣学辑要。备尽帝王学问之要。不下于大学衍义。东湖问答。可见明体适用之实。而四端七情诸书。足以断诸儒未定之论。其书具在。可考而知也。立朝以来。多退少进。晚被 宣庙殊眷。当癸未之变。受委本兵。吁谟密勿。动合机宜。 宣祖倚注弥重。益为群小所忌。阴构显斥。必欲置之不测。幸赖 圣鉴洞照。邪正自别。不幸无禄。未极毕展所学。有志之士。至今痛恨。成浑敦厚庄重。笃行力学。语默动静。一以小学家礼为准则。操守之严。不愧屋漏。孝悌之行。可通神明。德器成就。表里如一。故臣李珥每称其笃实以为不可及。早与李珥定交讲劘。志同道合。珥则出当世道。而浑屏处丘园。虽迫于 恩旨。时诣辇下。然其雅志长在山野。及癸未年间。李珥为群小所构。浑时在洛下。上章申辨。遂为一边人所仇嫉。初中李弘老之巧谮。卒被郑仁弘之丑诋。使 先王好贤之盛心。不得保全始终。抱冤泉壤。几数十年。逮我 圣明当宁。始得昭雪。呜呼。此实斯文隆替之会。夫岂容人力于其间哉。臣等窃念此二臣者。生五贤之后。讲明道学。发挥幽眇。凡理气离合四端七情等说。诸儒所论。互有得失。而反复
著述者击蒙要诀。极切于学者日用功程。而圣学辑要。备尽帝王学问之要。不下于大学衍义。东湖问答。可见明体适用之实。而四端七情诸书。足以断诸儒未定之论。其书具在。可考而知也。立朝以来。多退少进。晚被 宣庙殊眷。当癸未之变。受委本兵。吁谟密勿。动合机宜。 宣祖倚注弥重。益为群小所忌。阴构显斥。必欲置之不测。幸赖 圣鉴洞照。邪正自别。不幸无禄。未极毕展所学。有志之士。至今痛恨。成浑敦厚庄重。笃行力学。语默动静。一以小学家礼为准则。操守之严。不愧屋漏。孝悌之行。可通神明。德器成就。表里如一。故臣李珥每称其笃实以为不可及。早与李珥定交讲劘。志同道合。珥则出当世道。而浑屏处丘园。虽迫于 恩旨。时诣辇下。然其雅志长在山野。及癸未年间。李珥为群小所构。浑时在洛下。上章申辨。遂为一边人所仇嫉。初中李弘老之巧谮。卒被郑仁弘之丑诋。使 先王好贤之盛心。不得保全始终。抱冤泉壤。几数十年。逮我 圣明当宁。始得昭雪。呜呼。此实斯文隆替之会。夫岂容人力于其间哉。臣等窃念此二臣者。生五贤之后。讲明道学。发挥幽眇。凡理气离合四端七情等说。诸儒所论。互有得失。而反复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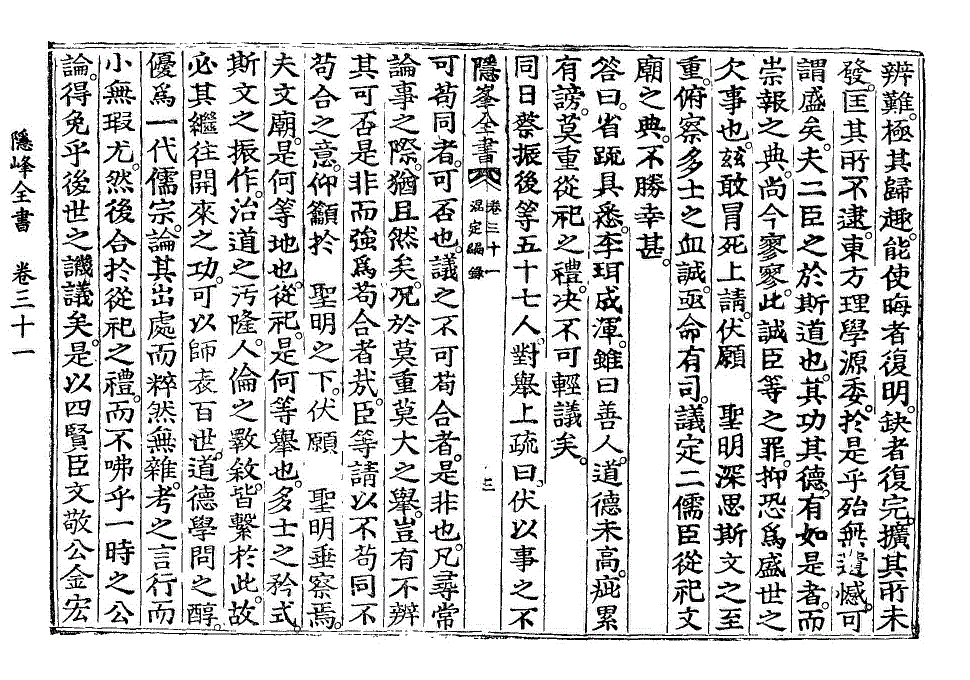 辨难。极其归趣。能使晦者复明。缺者复完。扩其所未发。匡其所不逮。东方理学源委。于是乎殆无遗憾。可谓盛矣。夫二臣之于斯道也。其功其德。有如是者。而崇报之典。尚今寥寥。此诚臣等之罪。抑恐为盛世之欠事也。兹敢冒死上请。伏愿 圣明深思斯文之至重。俯察多士之血诚。亟命有司。议定二儒臣从祀文庙之典。不胜幸甚。
辨难。极其归趣。能使晦者复明。缺者复完。扩其所未发。匡其所不逮。东方理学源委。于是乎殆无遗憾。可谓盛矣。夫二臣之于斯道也。其功其德。有如是者。而崇报之典。尚今寥寥。此诚臣等之罪。抑恐为盛世之欠事也。兹敢冒死上请。伏愿 圣明深思斯文之至重。俯察多士之血诚。亟命有司。议定二儒臣从祀文庙之典。不胜幸甚。答曰。省疏具悉。李珥成浑。虽曰善人。道德未高。疵累有谤。莫重从祀之礼。决不可轻议矣。
同日蔡振后等五十七人。对举上疏曰。伏以事之不可苟同者。可否也。议之不可苟合者。是非也。凡寻常论事之际。犹且然矣。况于莫重莫大之举。岂有不辨其可否是非而强为苟合者哉。臣等请以不苟同不苟合之意。仰吁于 圣明之下。伏愿 圣明垂察焉。夫文庙。是何等地也。从祀。是何等举也。多士之矜式。斯文之振作。治道之污隆。人伦之斁叙。皆击于此。故必其继往开来之功。可以师表百世。道德学问之醇。优为一代儒宗。论其出处而粹然无杂。考之言行而小无瑕尤。然后合于从祀之礼。而不咈乎一时之公论。得免乎后世之讥议矣。是以四贤臣文敬公金宏
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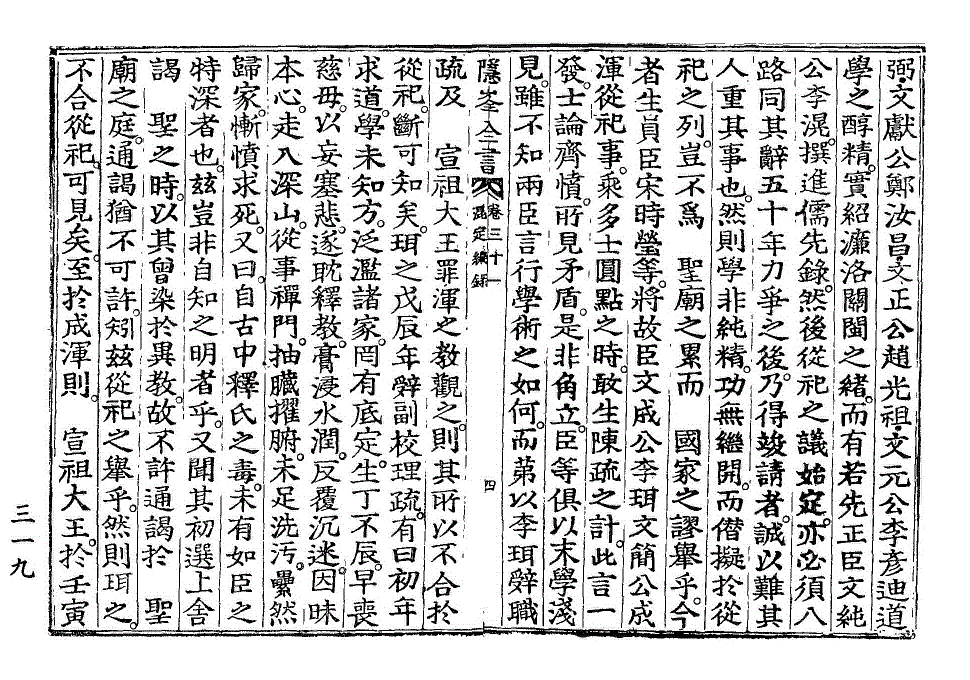 弼,文献公郑汝昌,文正公赵光祖,文元公李彦迪道学之醇精。实绍濂洛关闽之绪。而有若先正臣文纯公李滉。撰进儒先录。然后从祀之议始定。亦必须入路同其辞五十年力争之后。乃得竣请者。诚以难其人重其事也。然则学非纯精。功无继开。而僭拟于从祀之列。岂不为 圣庙之累而 国家之谬举乎。今者生员臣宋时莹等。将故臣文成公李珥文简公成浑从祀事。乘多士圆点之时。敢生陈疏之计。此言一发。士论齐愤。所见矛盾。是非角立。臣等俱以末学浅见。虽不知两臣言行学术之如何。而第以李珥辞职疏及 宣祖大王罪浑之教观之。则其所以不合于从祀。断可知矣。珥之戊辰年辞副校理疏。有曰初年求道。学未知方。泛滥诸家。罔有底定。生丁不辰。早丧慈毋。以妄塞悲。遂耽释教。膏浸水润。反覆沈迷。因昧本心。走入深山。从事禅门。抽脏擢腑。未足洗污。累然归家。惭愤求死。又曰。自古中释氏之毒。未有如臣之特深者也。玆岂非自知之明者乎。又闻其初选上舍谒 圣之时。以其曾染于异教。故不许通谒于 圣庙之庭。通谒犹不可许。矧玆从祀之举乎。然则珥之。不合从祀。可见矣。至于成浑则。 宣祖大王。于壬寅
弼,文献公郑汝昌,文正公赵光祖,文元公李彦迪道学之醇精。实绍濂洛关闽之绪。而有若先正臣文纯公李滉。撰进儒先录。然后从祀之议始定。亦必须入路同其辞五十年力争之后。乃得竣请者。诚以难其人重其事也。然则学非纯精。功无继开。而僭拟于从祀之列。岂不为 圣庙之累而 国家之谬举乎。今者生员臣宋时莹等。将故臣文成公李珥文简公成浑从祀事。乘多士圆点之时。敢生陈疏之计。此言一发。士论齐愤。所见矛盾。是非角立。臣等俱以末学浅见。虽不知两臣言行学术之如何。而第以李珥辞职疏及 宣祖大王罪浑之教观之。则其所以不合于从祀。断可知矣。珥之戊辰年辞副校理疏。有曰初年求道。学未知方。泛滥诸家。罔有底定。生丁不辰。早丧慈毋。以妄塞悲。遂耽释教。膏浸水润。反覆沈迷。因昧本心。走入深山。从事禅门。抽脏擢腑。未足洗污。累然归家。惭愤求死。又曰。自古中释氏之毒。未有如臣之特深者也。玆岂非自知之明者乎。又闻其初选上舍谒 圣之时。以其曾染于异教。故不许通谒于 圣庙之庭。通谒犹不可许。矧玆从祀之举乎。然则珥之。不合从祀。可见矣。至于成浑则。 宣祖大王。于壬寅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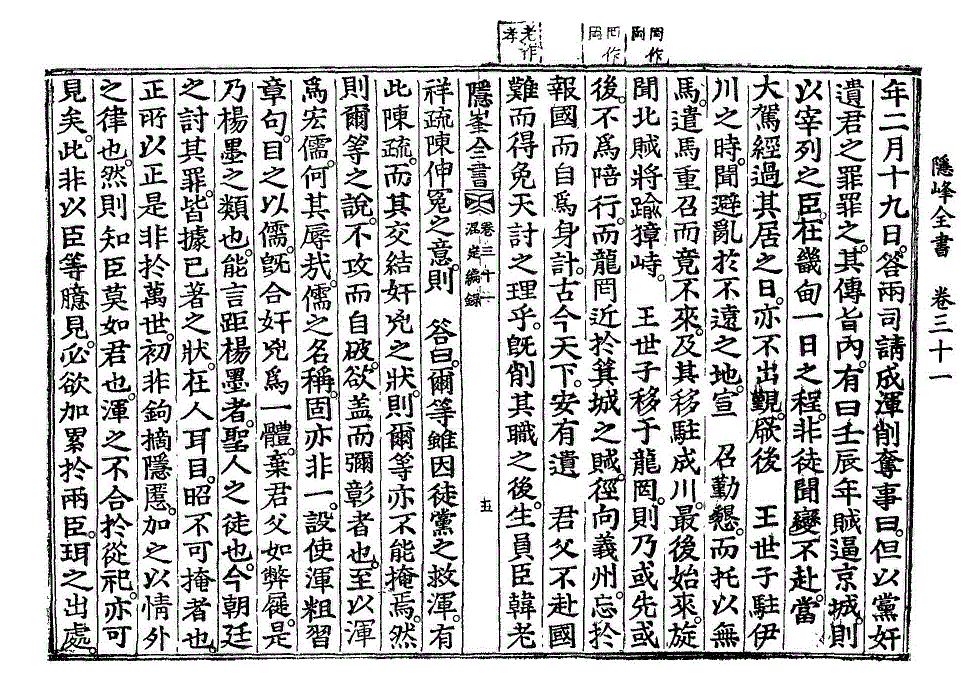 年二月十九日。答两司请成浑削夺事曰。但以党奸遗君之罪罪之。其传旨内。有曰壬辰年贼逼京城。则以宰列之臣。在畿甸一日之程。非徒闻变不赴。当。 大驾经过其居之日。亦不出觐。厥后 王世子驻伊川之时。闻避乱于不远之地。宣 召勤恳。而托以无马。遣马重召而竟不来。及其移驻成川。最后始来。旋闻北贼将踰獐峙。 王世子移于龙罔(罔作冈)。则乃或先或后。不为陪行。而龙罔(罔作冈)近于箕城之贼。径向义州。忘于报国而自为身计。古今天下。安有遗 君父不赴国难而得免天讨之理乎。既削其职之后。生员臣韩老(老作孝)祥疏陈伸冤之意。则 答曰。尔等虽因徒党之救浑。有此陈疏。而其交结奸凶之状。则尔等亦不能掩焉。然则尔等之说。不攻而自破。欲盖而弥彰者也。至以浑为宏儒。何其辱哉。儒之名称。固亦非一。设使浑粗习章句。目之以儒。既合奸凶为一体。弃君父如弊屣。是乃杨墨之类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今朝廷之讨其罪。皆据已著之状。在人耳目。昭不可掩者也。正所以正是非于万世。初非钩摘隐慝。加之以情外之律也。然则知臣莫如君也。浑之不合于从祀。亦可见矣。此非以臣等臆见。必欲加累于两臣。珥之出处。
年二月十九日。答两司请成浑削夺事曰。但以党奸遗君之罪罪之。其传旨内。有曰壬辰年贼逼京城。则以宰列之臣。在畿甸一日之程。非徒闻变不赴。当。 大驾经过其居之日。亦不出觐。厥后 王世子驻伊川之时。闻避乱于不远之地。宣 召勤恳。而托以无马。遣马重召而竟不来。及其移驻成川。最后始来。旋闻北贼将踰獐峙。 王世子移于龙罔(罔作冈)。则乃或先或后。不为陪行。而龙罔(罔作冈)近于箕城之贼。径向义州。忘于报国而自为身计。古今天下。安有遗 君父不赴国难而得免天讨之理乎。既削其职之后。生员臣韩老(老作孝)祥疏陈伸冤之意。则 答曰。尔等虽因徒党之救浑。有此陈疏。而其交结奸凶之状。则尔等亦不能掩焉。然则尔等之说。不攻而自破。欲盖而弥彰者也。至以浑为宏儒。何其辱哉。儒之名称。固亦非一。设使浑粗习章句。目之以儒。既合奸凶为一体。弃君父如弊屣。是乃杨墨之类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今朝廷之讨其罪。皆据已著之状。在人耳目。昭不可掩者也。正所以正是非于万世。初非钩摘隐慝。加之以情外之律也。然则知臣莫如君也。浑之不合于从祀。亦可见矣。此非以臣等臆见。必欲加累于两臣。珥之出处。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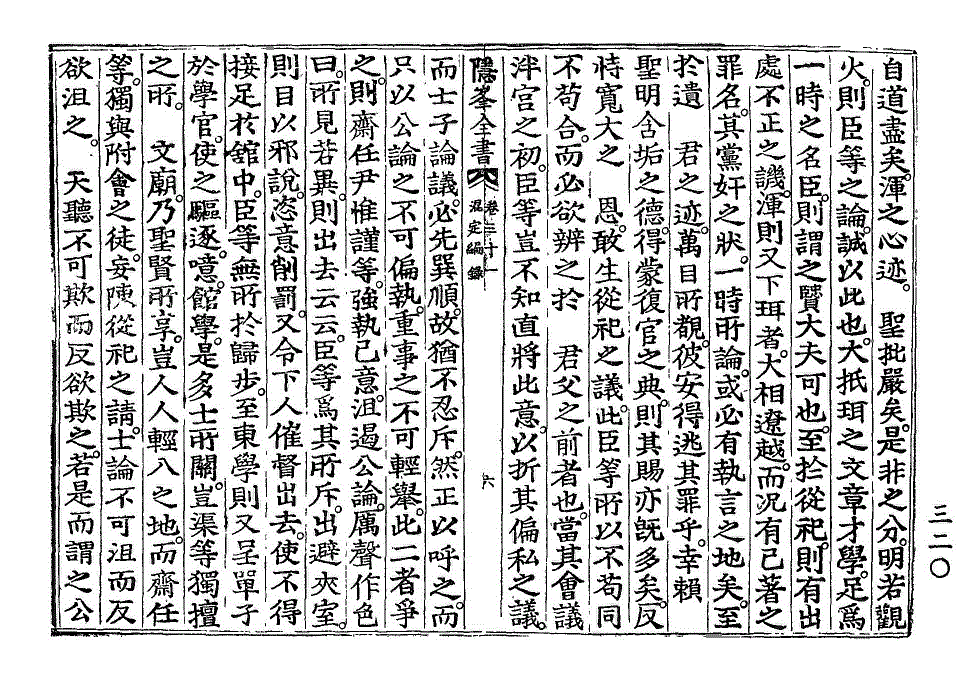 自道尽矣。浑之心迹。 圣批严矣。是非之分。明若观火。则臣等之论。诚以此也。大抵珥之文章才学。足为一时之名臣。则谓之贤大夫可也。至于从祀。则有出处不正之讥。浑则又下珥者。大相辽越。而况有已著之罪名。其党奸之状。一时所论。或必有执言之地矣。至于遗 君之迹。万目所睹。彼安得逃其罪乎。幸赖 圣明含垢之德。得蒙复官之典。则其赐亦既多矣。反恃宽大之 恩。敢生从祀之议。此臣等所以不苟同不苟合。而必欲辨之于 君父之前者也。当其会议泮宫之初。臣等岂不知直将此意。以折其偏私之议。而士子论议。必先巽顺。故犹不忍斥。然正以呼之。而只以公论之不可偏执。重事之不可轻举。此二者争之。则斋任尹惟谨等。强执己意。沮遏公论。厉声作色曰。所见若异。则出去云云。臣等为其所斥。出避夹室。则目以邪说。恣意削罚。又令下人催督出去。使不得接足于馆中。臣等无所于归步。至东学则又呈单子于学官。使之驱逐。噫。馆学。是多士所关。岂渠等独擅之所。 文庙。乃圣贤所享。岂人人轻入之地。而斋任等。独与附会之徒。妄陈从祀之请。士论不可沮而反欲沮之。 天听不可欺而反欲欺之。若是而谓之公
自道尽矣。浑之心迹。 圣批严矣。是非之分。明若观火。则臣等之论。诚以此也。大抵珥之文章才学。足为一时之名臣。则谓之贤大夫可也。至于从祀。则有出处不正之讥。浑则又下珥者。大相辽越。而况有已著之罪名。其党奸之状。一时所论。或必有执言之地矣。至于遗 君之迹。万目所睹。彼安得逃其罪乎。幸赖 圣明含垢之德。得蒙复官之典。则其赐亦既多矣。反恃宽大之 恩。敢生从祀之议。此臣等所以不苟同不苟合。而必欲辨之于 君父之前者也。当其会议泮宫之初。臣等岂不知直将此意。以折其偏私之议。而士子论议。必先巽顺。故犹不忍斥。然正以呼之。而只以公论之不可偏执。重事之不可轻举。此二者争之。则斋任尹惟谨等。强执己意。沮遏公论。厉声作色曰。所见若异。则出去云云。臣等为其所斥。出避夹室。则目以邪说。恣意削罚。又令下人催督出去。使不得接足于馆中。臣等无所于归步。至东学则又呈单子于学官。使之驱逐。噫。馆学。是多士所关。岂渠等独擅之所。 文庙。乃圣贤所享。岂人人轻入之地。而斋任等。独与附会之徒。妄陈从祀之请。士论不可沮而反欲沮之。 天听不可欺而反欲欺之。若是而谓之公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21H 页
 论。可乎。噫。从祀之举。果出于公共之论。则以士为名者。孰敢有异同之议。而今日之事。不可苟合。故先事而去者。连袂于桥门之外。其不去者。亦有郁抑之色。睢盱相视。气象骇异。菁莪乐育之地。反为排辄(辄作轧)之场。臣等非不知泯默各散。自为身谋。而顾以从祀重大之举。一失其宜。则学术之醇疵。士习之邪正。将至混淆莫辨。而斯文之害。有不可胜言者。故臣等为此力辨。俱被斥逐。岂徒臣等之不幸。抑亦国家之不幸也。臣等或在辇毂之下。或在岭海之远。今日一退。有怀不达。则是非不明于昭代。 圣庙受污于流辈。 列圣崇报之典。终归于不重之地。故群议所激。不能自抑。区区寸忱。敢渎于日月之明。伏愿 殿下审国家从祀之重。察臣等公共之议。则国家幸甚。斯文幸甚。
论。可乎。噫。从祀之举。果出于公共之论。则以士为名者。孰敢有异同之议。而今日之事。不可苟合。故先事而去者。连袂于桥门之外。其不去者。亦有郁抑之色。睢盱相视。气象骇异。菁莪乐育之地。反为排辄(辄作轧)之场。臣等非不知泯默各散。自为身谋。而顾以从祀重大之举。一失其宜。则学术之醇疵。士习之邪正。将至混淆莫辨。而斯文之害。有不可胜言者。故臣等为此力辨。俱被斥逐。岂徒臣等之不幸。抑亦国家之不幸也。臣等或在辇毂之下。或在岭海之远。今日一退。有怀不达。则是非不明于昭代。 圣庙受污于流辈。 列圣崇报之典。终归于不重之地。故群议所激。不能自抑。区区寸忱。敢渎于日月之明。伏愿 殿下审国家从祀之重。察臣等公共之议。则国家幸甚。斯文幸甚。答曰。省疏具悉。文成公李珥等从祀之请。殊极僭猥。予亦知其不可矣。
宋时莹等再疏。其略曰。臣等俱以蒙陋之质。久沐菁莪之化。不胜区区景贤之诚。沥血封章。冀以成 圣明崇儒重道之盛典。而微诚未孚。 圣批邈然。臣等聚首错愕。未晓 圣意之所在。既而。得见蔡振后等上疏草本。诬辞诐语。极其狼藉。虽范致虚。沈继祖之
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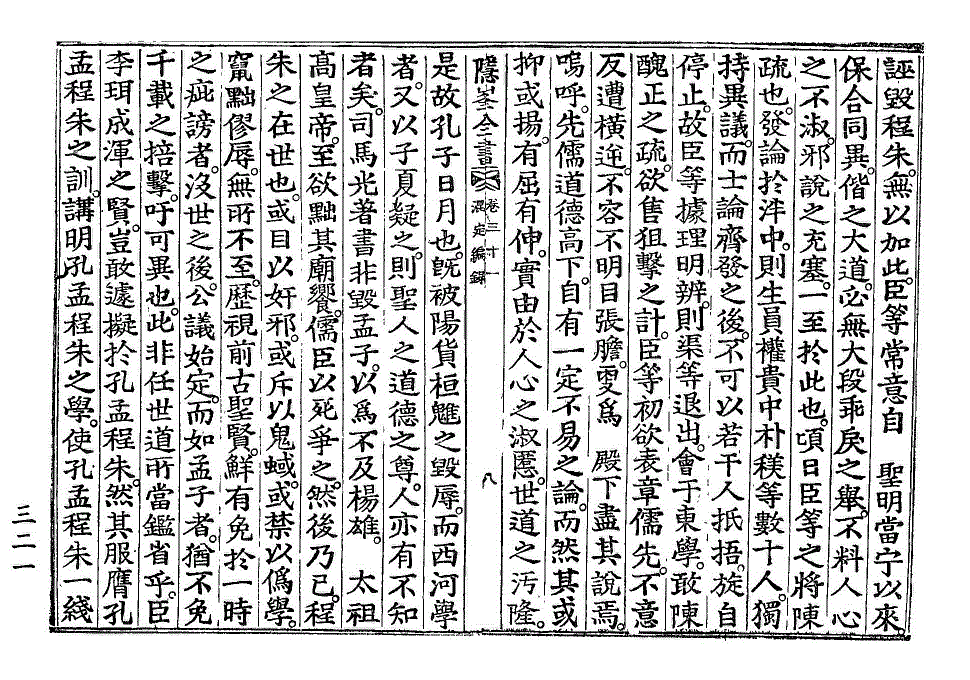 诬毁程朱。无以加此。臣等常意自 圣明当宁以来。保合同异。偕之大道。必无大段乖戾之举。不料人心之不淑。邪说之充塞。一至于此也。顷日臣等之将陈疏也。发论于泮中。则生员权贵中朴𥠦等数十人。独持异议。而士论齐发之后。不可以若干人抵捂。旋自停止。故臣等据理明辨。则渠等退出。会于东学。敢陈丑正之疏。欲售狙击之计。臣等初欲表章儒先。不意反遭横逆。不容不明目张胆。更为 殿下尽其说焉。呜呼。先儒道德高下。自有一定不易之论。而然其或抑或扬。有屈有伸。实由于人心之淑慝。世道之污隆。是故孔子日月也。既被阳货桓魋之毁辱。而西河学者。又以子夏疑之。则圣人之道德之尊。人亦有不知者矣。司马光著书非毁孟子。以为不及杨雄。 太祖高皇帝。至欲黜其庙飨。儒臣以死争之。然后乃已。程朱之在世也。或目以奸邪。或斥以鬼蜮。或禁以伪学。窜黜僇辱。无所不至。历视前古圣贤。鲜有免于一时之疵谤者。没世之后。公议始定。而如孟子者。犹不免千载之掊击。吁可异也。此非任世道所当鉴省乎。臣李珥成浑之贤。岂敢遽拟于孔孟程朱。然其服膺孔孟程朱之训。讲明孔孟程朱之学。使孔孟程朱一线
诬毁程朱。无以加此。臣等常意自 圣明当宁以来。保合同异。偕之大道。必无大段乖戾之举。不料人心之不淑。邪说之充塞。一至于此也。顷日臣等之将陈疏也。发论于泮中。则生员权贵中朴𥠦等数十人。独持异议。而士论齐发之后。不可以若干人抵捂。旋自停止。故臣等据理明辨。则渠等退出。会于东学。敢陈丑正之疏。欲售狙击之计。臣等初欲表章儒先。不意反遭横逆。不容不明目张胆。更为 殿下尽其说焉。呜呼。先儒道德高下。自有一定不易之论。而然其或抑或扬。有屈有伸。实由于人心之淑慝。世道之污隆。是故孔子日月也。既被阳货桓魋之毁辱。而西河学者。又以子夏疑之。则圣人之道德之尊。人亦有不知者矣。司马光著书非毁孟子。以为不及杨雄。 太祖高皇帝。至欲黜其庙飨。儒臣以死争之。然后乃已。程朱之在世也。或目以奸邪。或斥以鬼蜮。或禁以伪学。窜黜僇辱。无所不至。历视前古圣贤。鲜有免于一时之疵谤者。没世之后。公议始定。而如孟子者。犹不免千载之掊击。吁可异也。此非任世道所当鉴省乎。臣李珥成浑之贤。岂敢遽拟于孔孟程朱。然其服膺孔孟程朱之训。讲明孔孟程朱之学。使孔孟程朱一线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22H 页
 之道脉。赖不坠地。则是亦孔孟程朱之道也。孔孟程朱。既不免外至之诬。李珥成浑之见诋。诚有不足怪也。噫。李珥之贤。虽以振后辈。无他可指之疵。只举其小时从事禅门之事。为其瑕玷。流俗庸下之见。或有为此论者。臣等请辨之。禅门一法。虽曰异端。然其论心说性。实有精妙动人。故自昔真儒求道之初。例多流入于其中。张横渠程明道。其著者也。至于朱子。则最甚焉。年十五六。有志于道。而未得其方。求之于释氏。至以高僧道谦为师。沈溺不返者几十年。及年二十四。始得延平李先生而师事之。然后大悟禅学之非。延平与其友罗博文书曰。元晦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朱子集中。亦自屡陈少时学禅之事。以戒学者。夫儒释邪正。世之庸夫俗子。犹能言之。而程朱大贤。未免误入。何也。释氏之说。自有十分近理处。才质高明者。求道太切。用心过锐。易致流入。势固然矣。李珥之事。亦犹是也。此在李珥责己之道。宜有悔艾之心。自后学观之。惟当取其悟后造诣之高。以为师法。岂可指其迷时汎滥之失。议其疵累。必若以此为累。亦将并与朱子而攻之乎。振后疏中所谓李珥谒圣时不许通谒云者。此实无据之说。
之道脉。赖不坠地。则是亦孔孟程朱之道也。孔孟程朱。既不免外至之诬。李珥成浑之见诋。诚有不足怪也。噫。李珥之贤。虽以振后辈。无他可指之疵。只举其小时从事禅门之事。为其瑕玷。流俗庸下之见。或有为此论者。臣等请辨之。禅门一法。虽曰异端。然其论心说性。实有精妙动人。故自昔真儒求道之初。例多流入于其中。张横渠程明道。其著者也。至于朱子。则最甚焉。年十五六。有志于道。而未得其方。求之于释氏。至以高僧道谦为师。沈溺不返者几十年。及年二十四。始得延平李先生而师事之。然后大悟禅学之非。延平与其友罗博文书曰。元晦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朱子集中。亦自屡陈少时学禅之事。以戒学者。夫儒释邪正。世之庸夫俗子。犹能言之。而程朱大贤。未免误入。何也。释氏之说。自有十分近理处。才质高明者。求道太切。用心过锐。易致流入。势固然矣。李珥之事。亦犹是也。此在李珥责己之道。宜有悔艾之心。自后学观之。惟当取其悟后造诣之高。以为师法。岂可指其迷时汎滥之失。议其疵累。必若以此为累。亦将并与朱子而攻之乎。振后疏中所谓李珥谒圣时不许通谒云者。此实无据之说。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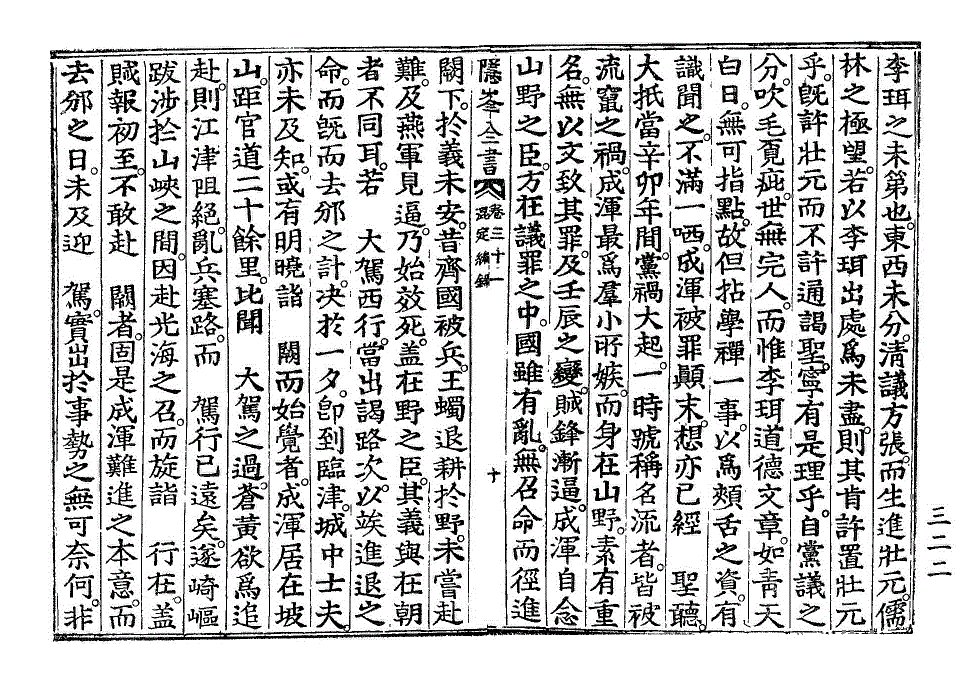 李珥之未第也。东西未分。清议方张。而生进壮元。儒林之极望。若以李珥出处为未尽。则其肯许置壮元乎。既许壮元而不许通谒圣。宁有是理乎。自党议之分。吹毛觅疵。世无完人。而惟李珥道德文章。如青天白日。无可指点。故但拈学禅一事。以为颊舌之资。有识闻之。不满一哂。成浑被罪颠末。想亦已经 圣听。大抵当辛卯年间。党祸大起。一时号称名流者。皆被流窜之祸。成浑最为群小所嫉。而身在山野。素有重名。无以文致其罪。及壬辰之变。贼锋渐逼。成浑自念山野之臣。方在议罪之中。国虽有乱。无召命而径进阙下。于义未安。昔齐国被兵。王蠋退耕于野。未尝赴难。及燕军见逼。乃始效死。盖在野之臣。其义与在朝者不同耳。若 大驾西行。当出谒路次。以俟进退之命。而既而去邠之计。决于一夕。即到临津。城中士夫。亦未及知。或有明晓诣 阙而始觉者。成浑居在坡山。距官道二十馀里。比闻 大驾之过。苍黄欲为追赴。则江津阻绝。乱兵塞路。而 驾行已远矣。遂崎岖跋涉于山峡之间。因赴光海之召。而旋诣 行在。盖贼报初至。不敢赴 阙者。固是成浑难进之本意。而去邠之日。未及迎 驾。实出于事势之无可奈何。非
李珥之未第也。东西未分。清议方张。而生进壮元。儒林之极望。若以李珥出处为未尽。则其肯许置壮元乎。既许壮元而不许通谒圣。宁有是理乎。自党议之分。吹毛觅疵。世无完人。而惟李珥道德文章。如青天白日。无可指点。故但拈学禅一事。以为颊舌之资。有识闻之。不满一哂。成浑被罪颠末。想亦已经 圣听。大抵当辛卯年间。党祸大起。一时号称名流者。皆被流窜之祸。成浑最为群小所嫉。而身在山野。素有重名。无以文致其罪。及壬辰之变。贼锋渐逼。成浑自念山野之臣。方在议罪之中。国虽有乱。无召命而径进阙下。于义未安。昔齐国被兵。王蠋退耕于野。未尝赴难。及燕军见逼。乃始效死。盖在野之臣。其义与在朝者不同耳。若 大驾西行。当出谒路次。以俟进退之命。而既而去邠之计。决于一夕。即到临津。城中士夫。亦未及知。或有明晓诣 阙而始觉者。成浑居在坡山。距官道二十馀里。比闻 大驾之过。苍黄欲为追赴。则江津阻绝。乱兵塞路。而 驾行已远矣。遂崎岖跋涉于山峡之间。因赴光海之召。而旋诣 行在。盖贼报初至。不敢赴 阙者。固是成浑难进之本意。而去邠之日。未及迎 驾。实出于事势之无可奈何。非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23H 页
 成浑之过也。贼臣李弘老。素嫉成浑。 宣庙至临津。问成浑家近远。弘老指近岸村舍曰。即此是也。 宣庙曰。然则何不来见。弘老曰。当此之时。渠安肯来谒。既而。成浑自光海所驻处。来谒 行在。弘老又进谗曰。成浑之来。为光海图内禅也。噫。曾母之信其子。犹有投杼之惑。况君臣之际。岂能无动于屡至之巧谗乎。继以有仁弘之诬构成罪案。振后疏中所举削夺传旨。此则成于仁弘之谗者也。呜呼。自古贤人君子。遭遇明主。终为谗邪离间者。何可胜道。前代之事。姑置勿论。且如本朝文正公臣赵光祖。受知 中庙。致尧舜之治。旋被不测之祸。至今为儒林之至痛。文元公臣李彦迪。三朝宿德。亦未免窜死遐荒。此岂 中明二圣之意。不过为奸人所构耳。若以一时被罪之故。便为百世是非之断案曰。斯人也曾在 先朝。被此罪名。知臣莫如君。不可更称其贤云。则赵光祖李彦迪。何以得预于斯文乎。 先朝五贤从祀之请。历四十馀年矣。 宣祖牢执不许。且下未安之严教。其时缙绅韦布之徒。齐声一心。为先贤卞白。何尝以 圣教如此。而遂沮已发之公论乎。惟仁弘之徒阴毁二贤者。雀跃而起。以为攘臂藉口之资。此士类之所
成浑之过也。贼臣李弘老。素嫉成浑。 宣庙至临津。问成浑家近远。弘老指近岸村舍曰。即此是也。 宣庙曰。然则何不来见。弘老曰。当此之时。渠安肯来谒。既而。成浑自光海所驻处。来谒 行在。弘老又进谗曰。成浑之来。为光海图内禅也。噫。曾母之信其子。犹有投杼之惑。况君臣之际。岂能无动于屡至之巧谗乎。继以有仁弘之诬构成罪案。振后疏中所举削夺传旨。此则成于仁弘之谗者也。呜呼。自古贤人君子。遭遇明主。终为谗邪离间者。何可胜道。前代之事。姑置勿论。且如本朝文正公臣赵光祖。受知 中庙。致尧舜之治。旋被不测之祸。至今为儒林之至痛。文元公臣李彦迪。三朝宿德。亦未免窜死遐荒。此岂 中明二圣之意。不过为奸人所构耳。若以一时被罪之故。便为百世是非之断案曰。斯人也曾在 先朝。被此罪名。知臣莫如君。不可更称其贤云。则赵光祖李彦迪。何以得预于斯文乎。 先朝五贤从祀之请。历四十馀年矣。 宣祖牢执不许。且下未安之严教。其时缙绅韦布之徒。齐声一心。为先贤卞白。何尝以 圣教如此。而遂沮已发之公论乎。惟仁弘之徒阴毁二贤者。雀跃而起。以为攘臂藉口之资。此士类之所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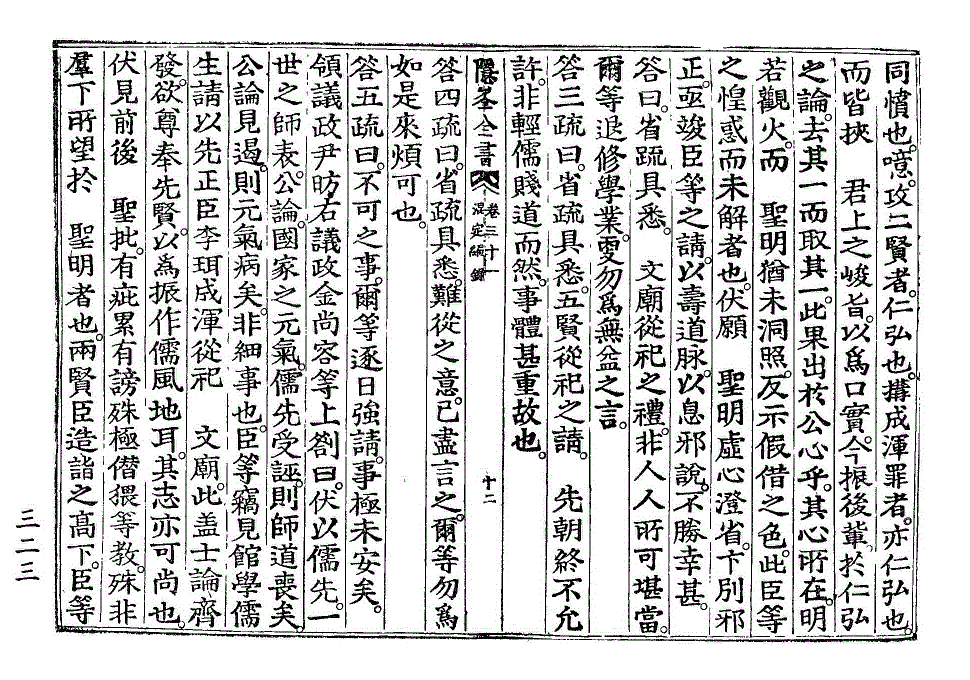 同愤也。噫。攻二贤者。仁弘也。构成浑罪者。亦仁弘也。而皆挟 君上之峻旨。以为口实。今振后辈。于仁弘之论。去其一而取其一。此果出于公心乎。其心所在。明若观火。而 圣明犹未洞照。反示假借之色。此臣等之惶惑而未解者也。伏愿 圣明虚心澄省。卞别邪正。亟竣臣等之请。以寿道脉。以息邪说。不胜幸甚。
同愤也。噫。攻二贤者。仁弘也。构成浑罪者。亦仁弘也。而皆挟 君上之峻旨。以为口实。今振后辈。于仁弘之论。去其一而取其一。此果出于公心乎。其心所在。明若观火。而 圣明犹未洞照。反示假借之色。此臣等之惶惑而未解者也。伏愿 圣明虚心澄省。卞别邪正。亟竣臣等之请。以寿道脉。以息邪说。不胜幸甚。答曰。省疏具悉。 文庙从祀之礼。非人人所可堪当。尔等退修学业。更勿为无益之言。
答三疏曰。省疏具悉。五贤从祀之请。 先朝终不允许。非轻儒贱道而然。事体甚重故也。
答四疏曰。省疏具悉。难从之意。已尽言之。尔等勿为如是来烦可也。
答五疏曰。不可之事。尔等逐日强请。事极未安矣。领议政尹昉,右议政金尚容等上劄曰。伏以儒先。一世之师表。公论。国家之元气。儒先受诬。则师道丧矣。公论见遏。则元气病矣。非细事也。臣等窃见馆学儒生请以先正臣李珥成浑从祀 文庙。此盖士论齐发。欲尊奉先贤。以为振作儒风地耳。其志亦可尚也。伏见前后 圣批。有疵累有谤殊极僭猥等教。殊非群下所望于 圣明者也。两贤臣造诣之高下。臣等
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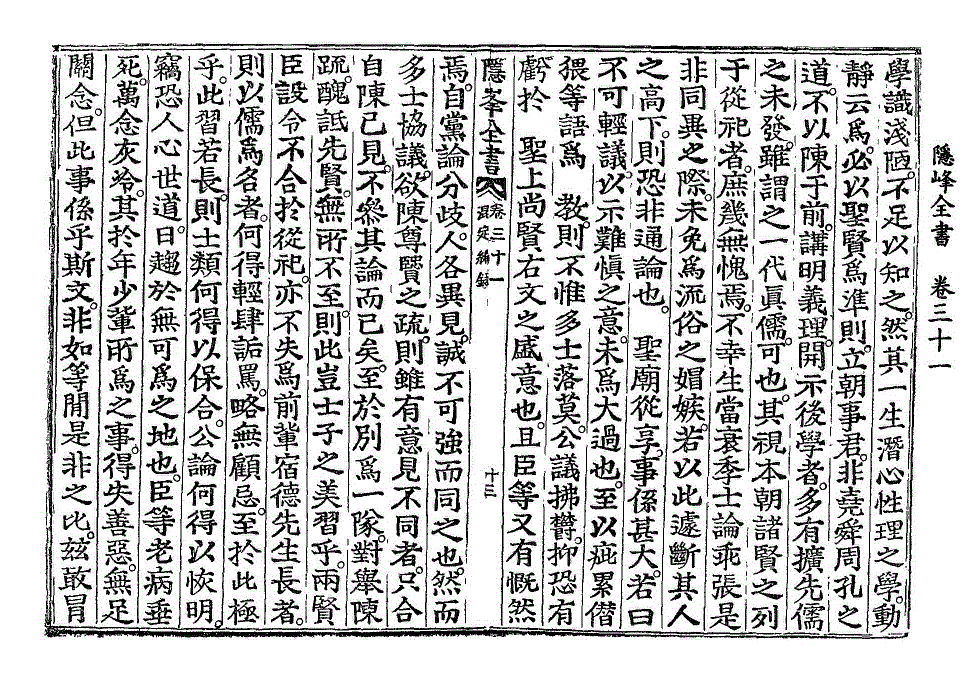 学识浅陋。不足以知之。然其一生潜心性理之学。动静云为。必以圣贤为准则。立朝事君。非尧舜周孔之道。不以陈于前。讲明义理。开示后学者。多有扩先儒之未发。虽谓之一代真儒。可也。其视本朝诸贤之列于从祀者。庶几无愧焉。不幸生当衰季士论乖张是非同异之际。未免为流俗之媢嫉。若以此遽断其人之高下。则恐非通论也。 圣庙从享。事系甚大。若曰不可轻议。以示难慎之意。未为大过也。至以疵累僭猥等语为 教。则不惟多士落莫。公议拂郁。抑恐有亏于 圣上尚贤右文之盛意也。且臣等又有慨然焉。自党论分岐。人各异见。诚不可强而同之也。然而多士协议。欲陈尊贤之疏。则虽有意见不同者。只合自陈己见。不参其论而已矣。至于别为一队。对举陈疏。丑诋先贤。无所不至。则此岂士子之美习乎。两贤臣设令不合于从祀。亦不失为前辈宿德先生长者。则以儒为各者。何得轻肆诟骂。略无顾忌。至于此极乎。此习若长。则士类何得以保合。公论何得以恢明。窃恐人心世道。日趋于无可为之地也。臣等老病垂死。万念灰冷。其于年少辈所为之事。得失善恶。无足关念。但此事系乎斯文。非如等閒是非之比。兹敢冒
学识浅陋。不足以知之。然其一生潜心性理之学。动静云为。必以圣贤为准则。立朝事君。非尧舜周孔之道。不以陈于前。讲明义理。开示后学者。多有扩先儒之未发。虽谓之一代真儒。可也。其视本朝诸贤之列于从祀者。庶几无愧焉。不幸生当衰季士论乖张是非同异之际。未免为流俗之媢嫉。若以此遽断其人之高下。则恐非通论也。 圣庙从享。事系甚大。若曰不可轻议。以示难慎之意。未为大过也。至以疵累僭猥等语为 教。则不惟多士落莫。公议拂郁。抑恐有亏于 圣上尚贤右文之盛意也。且臣等又有慨然焉。自党论分岐。人各异见。诚不可强而同之也。然而多士协议。欲陈尊贤之疏。则虽有意见不同者。只合自陈己见。不参其论而已矣。至于别为一队。对举陈疏。丑诋先贤。无所不至。则此岂士子之美习乎。两贤臣设令不合于从祀。亦不失为前辈宿德先生长者。则以儒为各者。何得轻肆诟骂。略无顾忌。至于此极乎。此习若长。则士类何得以保合。公论何得以恢明。窃恐人心世道。日趋于无可为之地也。臣等老病垂死。万念灰冷。其于年少辈所为之事。得失善恶。无足关念。但此事系乎斯文。非如等閒是非之比。兹敢冒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24L 页
 贡瞽说。伏愿 圣明深思长虑。亟示悔悟之意。使斯文吐气。则国家幸甚。儒林幸甚。取 进止。
贡瞽说。伏愿 圣明深思长虑。亟示悔悟之意。使斯文吐气。则国家幸甚。儒林幸甚。取 进止。答曰。省劄具悉。蔡振后等不俟国家处置。径先陈疏。殊甚浮妄矣。
左议政吴允谦上劄曰。伏以臣。蛰伏郊外。病势渐重。与死为邻。无所问闻。前日于邸报中。伏见 答馆儒宋时莹之批曰。疵累有谤。又 答蔡振后之批曰。殊极僭猥。臣不胜惊叹。尝窃以为 殿下于李珥成浑学问道德之盛。 先王际会眷遇之隆。末年遭谗被诬之由。或因筵臣前席之陈启。或因记实状德之文字。或因论辨著述之书。必以深察而明辨之矣。不意今者。有此未安之 教。有若全无敬慕尊信之心者焉。臣实未知 圣意所在也。君心万化之本源。儒贤国家之元气。 殿下于好善恶恶之分。不能诚知。而实见如此。则非但本源之忧有不可胜言。元气之受伤。国家之不幸。为如何也。臣最后得见蔡振后等诋诬两贤臣之疏。腾书李珥返道之后悔悟自列之章。成浑被诬之日论罪之 旨。以为證案。其构捏眩乱之状。极其狼藉。人心之不淑。士习之乖悖。良可痛心。臣。成浑门人也。详知成浑心事。只有老臣在耳。请陈
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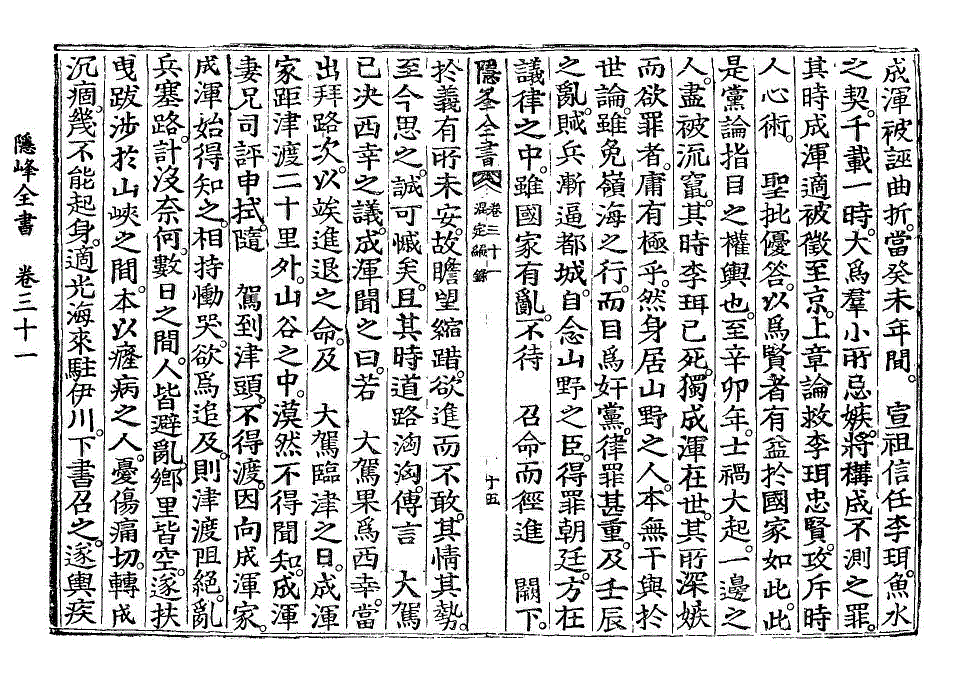 成浑被诬曲折。当癸未年间。 宣祖信任李珥。鱼水之契。千载一时。大为群小所忌嫉。将构成不测之罪。其时成浑适被徵至京。上章论救李珥忠贤。攻斥时人心术。 圣批优答。以为贤者有益于国家如此。此是党论指目之权舆也。至辛卯年。士祸大起。一边之人。尽被流窜。其时李珥已死。独成浑在世。其所深嫉而欲罪者。庸有极乎。然身居山野之人。本无干与于世论。虽免岭海之行。而目为奸党。律罪甚重。及壬辰之乱。贼兵渐逼都城。自念山野之臣。得罪朝廷。方在议律之中。虽国家有乱。不待 召命而径进 阙下。于义有所未安。故瞻望缩踖。欲进而不敢。其情其势。至今思之。诚可戚矣。且其时道路汹汹。传言 大驾已决西幸之议。成浑闻之曰。若 大驾果为西幸。当出拜路次。以俟进退之命。及 大驾临津之日。成浑家距津渡二十里外。山谷之中。漠然不得闻知。成浑妻兄司评申拭。随 驾到津头。不得渡。因向成浑家。成浑始得知之。相持恸哭。欲为追及。则津渡阻绝。乱兵塞路。计没奈何。数日之间。人皆避乱。乡里皆空。遂扶曳跋涉于山峡之间。本以癃病之人。忧伤痛切。转成沈痼。几不能起身。适光海来驻伊川。下书召之。遂舆疾
成浑被诬曲折。当癸未年间。 宣祖信任李珥。鱼水之契。千载一时。大为群小所忌嫉。将构成不测之罪。其时成浑适被徵至京。上章论救李珥忠贤。攻斥时人心术。 圣批优答。以为贤者有益于国家如此。此是党论指目之权舆也。至辛卯年。士祸大起。一边之人。尽被流窜。其时李珥已死。独成浑在世。其所深嫉而欲罪者。庸有极乎。然身居山野之人。本无干与于世论。虽免岭海之行。而目为奸党。律罪甚重。及壬辰之乱。贼兵渐逼都城。自念山野之臣。得罪朝廷。方在议律之中。虽国家有乱。不待 召命而径进 阙下。于义有所未安。故瞻望缩踖。欲进而不敢。其情其势。至今思之。诚可戚矣。且其时道路汹汹。传言 大驾已决西幸之议。成浑闻之曰。若 大驾果为西幸。当出拜路次。以俟进退之命。及 大驾临津之日。成浑家距津渡二十里外。山谷之中。漠然不得闻知。成浑妻兄司评申拭。随 驾到津头。不得渡。因向成浑家。成浑始得知之。相持恸哭。欲为追及。则津渡阻绝。乱兵塞路。计没奈何。数日之间。人皆避乱。乡里皆空。遂扶曳跋涉于山峡之间。本以癃病之人。忧伤痛切。转成沈痼。几不能起身。适光海来驻伊川。下书召之。遂舆疾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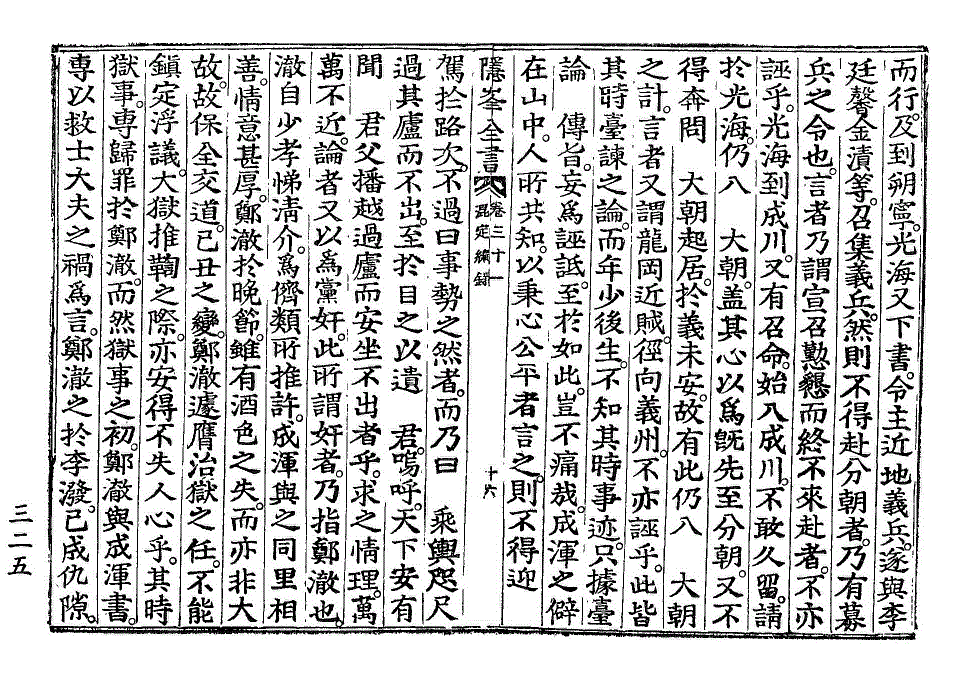 而行。及到朔宁。光海又下书。令主近地义兵。遂与李廷馨,金渍等。召集义兵。然则不得赴分朝者。乃有募兵之令也。言者乃谓宣召勤恳而终不来赴者。不亦诬乎。光海到成川。又有召命。始入成川。不敢久留。请于光海。仍入 大朝。盖其心以为既先至分朝。又不得奔问 大朝起居。于义未安。故有此仍入 大朝之计。言者又谓龙冈近贼。径向义州。不亦诬乎。此皆其时台谏之论。而年少后生。不知其时事迹。只据台论 传旨。妄为诬诋。至于如此。岂不痛哉。成浑之僻在山中。人所共知。以秉心公平者言之。则不得迎 驾于路次。不过曰事势之然者。而乃曰 乘舆咫尺过其庐而不出。至于目之以遗 君。呜呼。天下安有闻 君父播越过庐而安坐不出者乎。求之情理。万万不近。论者又以为党奸。此所谓奸者。乃指郑澈也。澈自少孝悌清介。为侪类所推许。成浑与之同里相善。情意甚厚。郑澈于晚节。虽有酒色之失。而亦非大故。故保全交道。己丑之变。郑澈遽膺治狱之任。不能镇定浮议。大狱推鞫之际。亦安得不失人心乎。其时狱事。专归罪于郑澈。而然狱事之初。郑澈与成浑书。专以救士大夫之祸为言。郑澈之于李泼。已成仇隙。
而行。及到朔宁。光海又下书。令主近地义兵。遂与李廷馨,金渍等。召集义兵。然则不得赴分朝者。乃有募兵之令也。言者乃谓宣召勤恳而终不来赴者。不亦诬乎。光海到成川。又有召命。始入成川。不敢久留。请于光海。仍入 大朝。盖其心以为既先至分朝。又不得奔问 大朝起居。于义未安。故有此仍入 大朝之计。言者又谓龙冈近贼。径向义州。不亦诬乎。此皆其时台谏之论。而年少后生。不知其时事迹。只据台论 传旨。妄为诬诋。至于如此。岂不痛哉。成浑之僻在山中。人所共知。以秉心公平者言之。则不得迎 驾于路次。不过曰事势之然者。而乃曰 乘舆咫尺过其庐而不出。至于目之以遗 君。呜呼。天下安有闻 君父播越过庐而安坐不出者乎。求之情理。万万不近。论者又以为党奸。此所谓奸者。乃指郑澈也。澈自少孝悌清介。为侪类所推许。成浑与之同里相善。情意甚厚。郑澈于晚节。虽有酒色之失。而亦非大故。故保全交道。己丑之变。郑澈遽膺治狱之任。不能镇定浮议。大狱推鞫之际。亦安得不失人心乎。其时狱事。专归罪于郑澈。而然狱事之初。郑澈与成浑书。专以救士大夫之祸为言。郑澈之于李泼。已成仇隙。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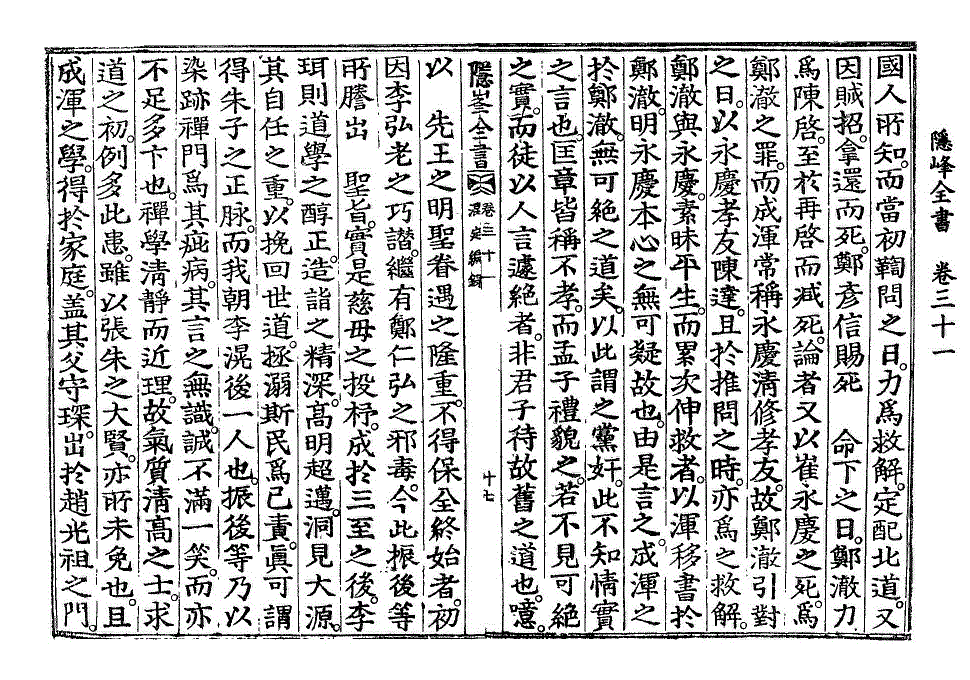 国人所知。而当初鞫问之日。力为救解。定配北道。又因贼招。拿还而死。郑彦信赐死 命下之日。郑澈力为陈启。至于再启而减死。论者又以崔永庆之死。为郑澈之罪。而成浑常称永庆清修孝友。故郑澈引对之日。以永庆孝友陈达。且于推问之时。亦为之救解。郑澈与永庆。素昧平生。而累次伸救者。以浑移书于郑澈。明永庆本心之无可疑故也。由是言之。成浑之于郑澈。无可绝之道矣。以此谓之党奸。此不知情实之言也。匡章皆称不孝。而孟子礼貌之。若不见可绝之实。而徒以人言遽绝者。非君子待故旧之道也。噫。以 先王之明圣眷遇之隆重。不得保全终始者。初因李弘老之巧谮。继有郑仁弘之邪毒。今此振后等所誊胜出 圣旨。实是慈母之投杼。成于三至之后。李珥则道学之醇正。造诣之精深。高明超迈。洞见大源。其自任之重。以挽回世道。拯溺斯民为己责。真可谓得朱子之正脉。而我朝李滉后一人也。振后等乃以染迹禅门为其疵病。其言之无识。诚不满一笑。而亦不足多卞也。禅学清静而近理。故气质清高之士。求道之初。例多此患。虽以张朱之大贤。亦所未免也。且成浑之学。得于家庭。盖其父守琛。出于赵光祖之门。
国人所知。而当初鞫问之日。力为救解。定配北道。又因贼招。拿还而死。郑彦信赐死 命下之日。郑澈力为陈启。至于再启而减死。论者又以崔永庆之死。为郑澈之罪。而成浑常称永庆清修孝友。故郑澈引对之日。以永庆孝友陈达。且于推问之时。亦为之救解。郑澈与永庆。素昧平生。而累次伸救者。以浑移书于郑澈。明永庆本心之无可疑故也。由是言之。成浑之于郑澈。无可绝之道矣。以此谓之党奸。此不知情实之言也。匡章皆称不孝。而孟子礼貌之。若不见可绝之实。而徒以人言遽绝者。非君子待故旧之道也。噫。以 先王之明圣眷遇之隆重。不得保全终始者。初因李弘老之巧谮。继有郑仁弘之邪毒。今此振后等所誊胜出 圣旨。实是慈母之投杼。成于三至之后。李珥则道学之醇正。造诣之精深。高明超迈。洞见大源。其自任之重。以挽回世道。拯溺斯民为己责。真可谓得朱子之正脉。而我朝李滉后一人也。振后等乃以染迹禅门为其疵病。其言之无识。诚不满一笑。而亦不足多卞也。禅学清静而近理。故气质清高之士。求道之初。例多此患。虽以张朱之大贤。亦所未免也。且成浑之学。得于家庭。盖其父守琛。出于赵光祖之门。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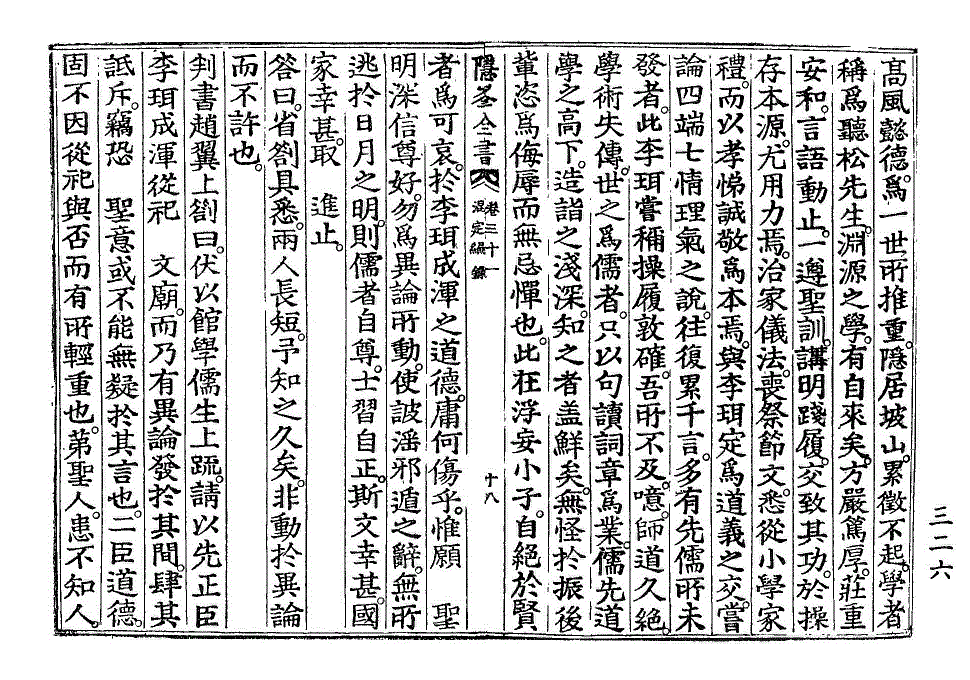 高风懿德。为一世所推重。隐居坡山。累徵不起。学者称为听松先生。渊源之学。有自来矣。方严笃厚。庄重安和。言语动止。一遵圣训。讲明践履。交致其功。于操存本源。尤用力焉。治家仪法。丧祭节文。悉从小学家礼。而以孝悌诚敬为本焉。与李珥定为道义之交。尝论四端七情理气之说。往复累千言。多有先儒所未发者。此李珥尝称操履敦确。吾所不及。噫。师道久绝。学术失传。世之为儒者。只以句读词章为业。儒先道学之高下。造诣之浅深。知之者盖鲜矣。无怪于振后辈恣为侮辱而无忌惮也。此在浮妄小子。自绝于贤者为可哀。于李珥成浑之道德。庸何伤乎。惟愿 圣明深信尊好。勿为异论所动。使诐淫邪遁之辞。无所逃于日月之明。则儒者自尊。士习自正。斯文幸甚。国家幸甚。取 进止。
高风懿德。为一世所推重。隐居坡山。累徵不起。学者称为听松先生。渊源之学。有自来矣。方严笃厚。庄重安和。言语动止。一遵圣训。讲明践履。交致其功。于操存本源。尤用力焉。治家仪法。丧祭节文。悉从小学家礼。而以孝悌诚敬为本焉。与李珥定为道义之交。尝论四端七情理气之说。往复累千言。多有先儒所未发者。此李珥尝称操履敦确。吾所不及。噫。师道久绝。学术失传。世之为儒者。只以句读词章为业。儒先道学之高下。造诣之浅深。知之者盖鲜矣。无怪于振后辈恣为侮辱而无忌惮也。此在浮妄小子。自绝于贤者为可哀。于李珥成浑之道德。庸何伤乎。惟愿 圣明深信尊好。勿为异论所动。使诐淫邪遁之辞。无所逃于日月之明。则儒者自尊。士习自正。斯文幸甚。国家幸甚。取 进止。答曰。省劄具悉。两人长短。予知之久矣。非动于异论而不许也。
判书赵翼上劄曰。伏以馆学儒生上疏。请以先正臣李珥成浑从祀 文庙。而乃有异论发于其间。肆其诋斥。窃恐 圣意或不能无疑于其言也。二臣道德。固不因从祀与否而有所轻重也。第圣人。患不知人。
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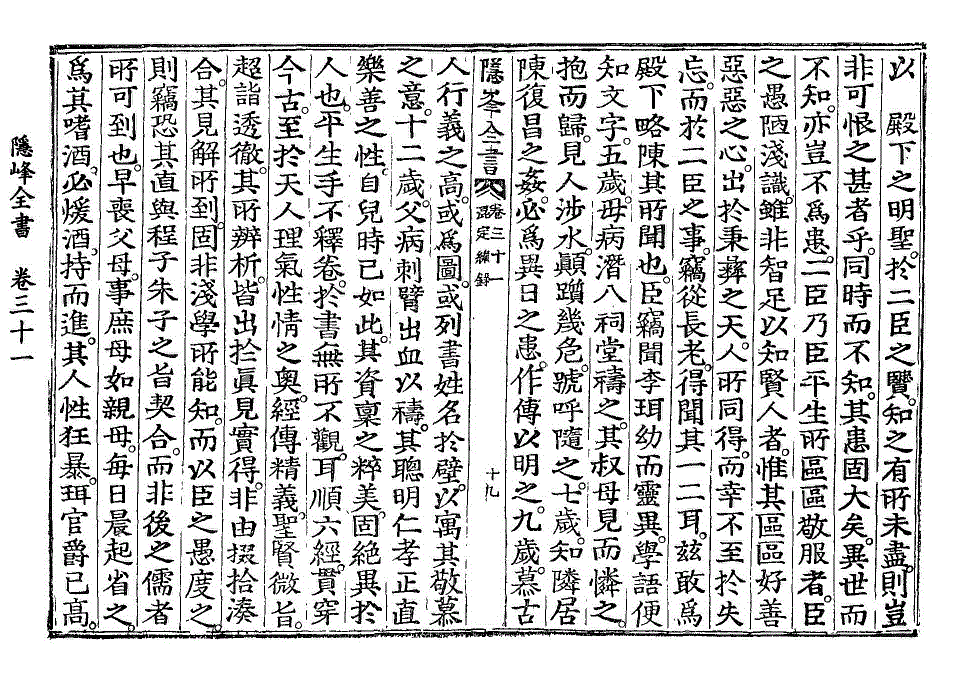 以 殿下之明圣。于二臣之贤。知之有所未尽。则岂非可恨之甚者乎。同时而不知。其患固大矣。异世而不知。亦岂不为患。二臣乃臣平生所区区敬服者。臣之愚陋浅识。虽非智足以知贤人者。惟其区区好善恶恶之心。出于秉彝之天。人所同得。而幸不至于失忘。而于二臣之事。窃从长老。得闻其一二耳。玆敢为殿下略陈其所闻也。臣窃闻李珥幼而灵异。学语便知文字。五岁。母病潜入祠堂祷之。其叔母见而怜之。抱而归。见人涉水。颠踬几危。号呼随之。七岁。知邻居陈复昌之奸。必为异日之患。作传以明之。九岁。慕古人行义之高。或为图。或列书姓名于壁。以寓其敬慕之意。十二岁。父病刺臂出血以祷。其聪明仁孝正直乐善之性。自儿时已如此。其资禀之粹美。固绝异于人也。平生手不释卷。于书无所不观。耳顺六经。贯穿今古。至于天人理气性情之奥。经传精义。圣贤微旨。超诣透彻。其所辨析。皆出于真见实得。非由掇拾凑合。其见解所到。固非浅学所能知。而以臣之愚度之。则窃恐其直与程子朱子之旨契合。而非后之儒者所可到也。早丧父母。事庶母如亲母。每日晨起省之。为其嗜酒。必煖酒。持而进。其人性狂暴。珥官爵已高。
以 殿下之明圣。于二臣之贤。知之有所未尽。则岂非可恨之甚者乎。同时而不知。其患固大矣。异世而不知。亦岂不为患。二臣乃臣平生所区区敬服者。臣之愚陋浅识。虽非智足以知贤人者。惟其区区好善恶恶之心。出于秉彝之天。人所同得。而幸不至于失忘。而于二臣之事。窃从长老。得闻其一二耳。玆敢为殿下略陈其所闻也。臣窃闻李珥幼而灵异。学语便知文字。五岁。母病潜入祠堂祷之。其叔母见而怜之。抱而归。见人涉水。颠踬几危。号呼随之。七岁。知邻居陈复昌之奸。必为异日之患。作传以明之。九岁。慕古人行义之高。或为图。或列书姓名于壁。以寓其敬慕之意。十二岁。父病刺臂出血以祷。其聪明仁孝正直乐善之性。自儿时已如此。其资禀之粹美。固绝异于人也。平生手不释卷。于书无所不观。耳顺六经。贯穿今古。至于天人理气性情之奥。经传精义。圣贤微旨。超诣透彻。其所辨析。皆出于真见实得。非由掇拾凑合。其见解所到。固非浅学所能知。而以臣之愚度之。则窃恐其直与程子朱子之旨契合。而非后之儒者所可到也。早丧父母。事庶母如亲母。每日晨起省之。为其嗜酒。必煖酒。持而进。其人性狂暴。珥官爵已高。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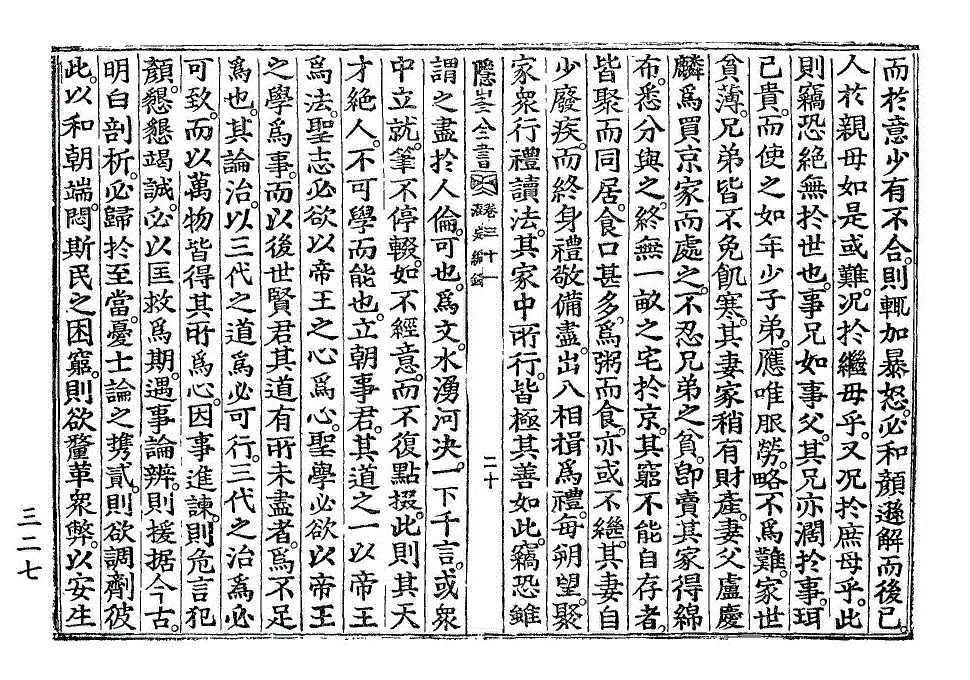 而于意少有不合。则辄加暴怒。必和颜逊解而后已。人于亲毋如是或难。况于继母乎。又况于庶母乎。此则窃恐绝无于世也。事兄如事父。其兄亦阔于事。珥已贵。而使之如年少子弟。应唯服劳。略不为难。家世贫薄。兄弟皆不免饥寒。其妻家稍有财产。妻父卢庆麟为买京家而处之。不忍兄弟之贫。即卖其家得绵布。悉分与之。终无一亩之宅于京。其穷不能自存者。皆聚而同居。食口甚多。为粥而食。亦或不继。其妻自少废疾。而终身礼敬备尽。出入相揖为礼。每朔望。聚家众行礼读法。其家中所行。皆极其善如此。窃恐虽谓之尽于人伦。可也。为文。水涌河决。一下千言。或众中立就。笔不停辍。如不经意。而不复点掇。此则其天才绝人。不可学而能也。立朝事君。其道之一以帝王为法。圣志必欲以帝王之心为心。圣学必欲以帝王之学为事。而以后世贤君其道有所未尽者。为不足为也。其论治。以三代之道为必可行。三代之治为必可致。而以万物皆得其所为心。因事进谏。则危言犯颜。恳恳竭诚。必以匡救为期。遇事论辨。则援据今古。明白剖析。必归于至当。忧士论之携贰。则欲调剂彼此。以和朝端。闷斯民之困穷。则欲釐革众弊。以安生
而于意少有不合。则辄加暴怒。必和颜逊解而后已。人于亲毋如是或难。况于继母乎。又况于庶母乎。此则窃恐绝无于世也。事兄如事父。其兄亦阔于事。珥已贵。而使之如年少子弟。应唯服劳。略不为难。家世贫薄。兄弟皆不免饥寒。其妻家稍有财产。妻父卢庆麟为买京家而处之。不忍兄弟之贫。即卖其家得绵布。悉分与之。终无一亩之宅于京。其穷不能自存者。皆聚而同居。食口甚多。为粥而食。亦或不继。其妻自少废疾。而终身礼敬备尽。出入相揖为礼。每朔望。聚家众行礼读法。其家中所行。皆极其善如此。窃恐虽谓之尽于人伦。可也。为文。水涌河决。一下千言。或众中立就。笔不停辍。如不经意。而不复点掇。此则其天才绝人。不可学而能也。立朝事君。其道之一以帝王为法。圣志必欲以帝王之心为心。圣学必欲以帝王之学为事。而以后世贤君其道有所未尽者。为不足为也。其论治。以三代之道为必可行。三代之治为必可致。而以万物皆得其所为心。因事进谏。则危言犯颜。恳恳竭诚。必以匡救为期。遇事论辨。则援据今古。明白剖析。必归于至当。忧士论之携贰。则欲调剂彼此。以和朝端。闷斯民之困穷。则欲釐革众弊。以安生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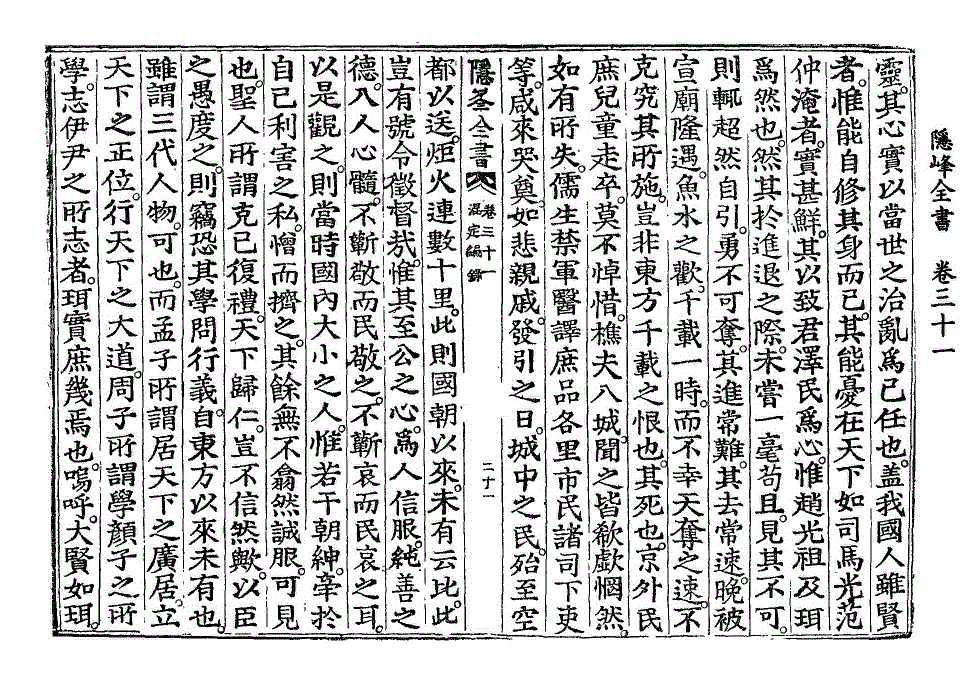 灵。其心实以当世之治乱为己任也。盖我国人虽贤者。惟能自修其身而已。其能忧在天下如司马光,范仲淹者。实甚鲜。其以致君泽民为心。惟赵光祖及珥为然也。然其于进退之际。未尝一毫苟且。见其不可。则辄超然自引。勇不可夺。其进常难。其去常速。晚被宣庙隆遇。鱼水之欢。千载一时。而不幸天夺之速。不克究其所施。岂非东方千载之恨也。其死也。京外民庶儿童走卒。莫不悼惜。樵夫入城。闻之皆欷歔惘然。如有所失。儒生禁军医译庶品各里市民诸司下吏等。咸来哭奠。如悲亲戚。发引之日。城中之民。殆至空都以送。炬火连数十里。此则国朝以来。未有云比。此岂有号令徵督哉。惟其至公之心。为人信服。纯善之德。入人心髓。不蕲敬而民敬之。不蕲哀而民哀之耳。以是观之。则当时国内大小之人。惟若干朝绅。牵于自己利害之私。憎而挤之。其馀无不翕然诚服。可见也。圣人所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岂不信然欤。以臣之愚度之。则窃恐其学问行义。自东方以来未有也。虽谓三代人物。可也。而孟子所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周子所谓学颜子之所学。志伊尹之所志者。珥实庶几焉也。呜呼。大贤如珥。
灵。其心实以当世之治乱为己任也。盖我国人虽贤者。惟能自修其身而已。其能忧在天下如司马光,范仲淹者。实甚鲜。其以致君泽民为心。惟赵光祖及珥为然也。然其于进退之际。未尝一毫苟且。见其不可。则辄超然自引。勇不可夺。其进常难。其去常速。晚被宣庙隆遇。鱼水之欢。千载一时。而不幸天夺之速。不克究其所施。岂非东方千载之恨也。其死也。京外民庶儿童走卒。莫不悼惜。樵夫入城。闻之皆欷歔惘然。如有所失。儒生禁军医译庶品各里市民诸司下吏等。咸来哭奠。如悲亲戚。发引之日。城中之民。殆至空都以送。炬火连数十里。此则国朝以来。未有云比。此岂有号令徵督哉。惟其至公之心。为人信服。纯善之德。入人心髓。不蕲敬而民敬之。不蕲哀而民哀之耳。以是观之。则当时国内大小之人。惟若干朝绅。牵于自己利害之私。憎而挤之。其馀无不翕然诚服。可见也。圣人所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岂不信然欤。以臣之愚度之。则窃恐其学问行义。自东方以来未有也。虽谓三代人物。可也。而孟子所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周子所谓学颜子之所学。志伊尹之所志者。珥实庶几焉也。呜呼。大贤如珥。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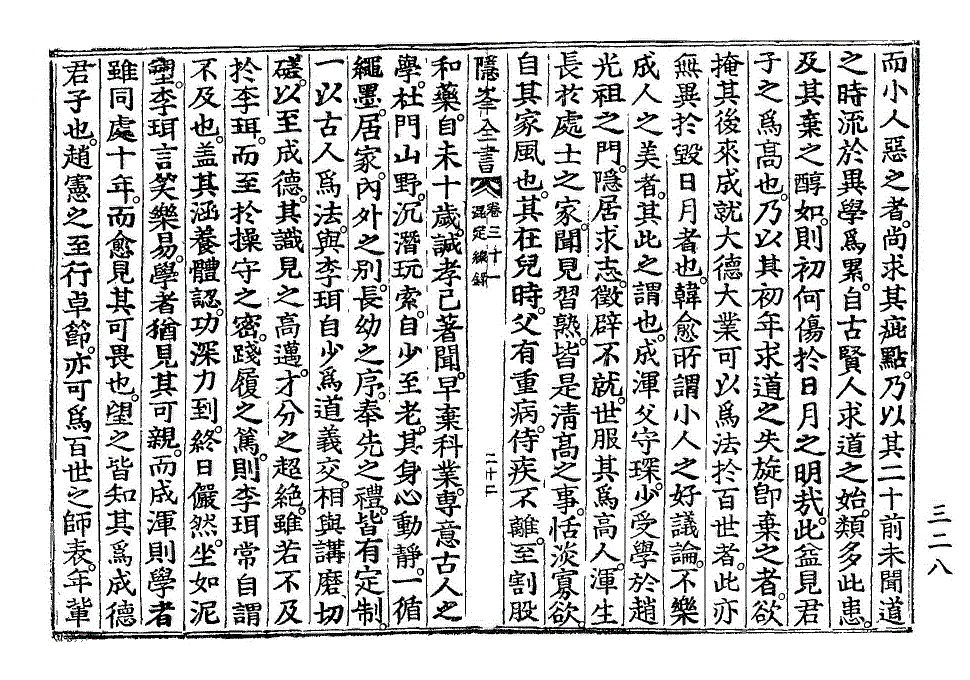 而小人恶之者。尚求其疵点。乃以其二十前未闻道之时流于异学为累。自古贤人求道之始。类多此患。及其弃之醇如。则初何伤于日月之明哉。此益见君子之为高也。乃以其初年求道之失旋即弃之者。欲掩其后来成就大德大业可以为法于百世者。此亦无异于毁日月者也。韩愈所谓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者。其此之谓也。成浑父守琛。少受学于赵光祖之门。隐居求志。徵辟不就。世服其为高人。浑生长于处士之家。闻见习熟。皆是清高之事。恬淡寡欲。自其家风也。其在儿时。父有重病。侍疾不离。至割股和药。自未十岁。诚孝已著闻。早弃科业。专意古人之学。杜门山野。沈潜玩索。自少至老。其身心动静。一循绳墨。居家。内外之别。长幼之序。奉先之礼。皆有定制。一以古人为法。与李珥自少为道义交。相与讲磨切磋。以至成德。其识见之高迈。才分之超绝。虽若不及于李珥。而至于操守之密。践履之笃。则李珥常自谓不及也。盖其涵养体认。功深力到。终日俨然。坐如泥塑。李珥言笑乐易。学者犹见其可亲。而成浑则学者虽同处十年。而愈见其可畏也。望之皆知其为成德君子也。赵宪之至行卓节。亦可为百世之师表。年辈
而小人恶之者。尚求其疵点。乃以其二十前未闻道之时流于异学为累。自古贤人求道之始。类多此患。及其弃之醇如。则初何伤于日月之明哉。此益见君子之为高也。乃以其初年求道之失旋即弃之者。欲掩其后来成就大德大业可以为法于百世者。此亦无异于毁日月者也。韩愈所谓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者。其此之谓也。成浑父守琛。少受学于赵光祖之门。隐居求志。徵辟不就。世服其为高人。浑生长于处士之家。闻见习熟。皆是清高之事。恬淡寡欲。自其家风也。其在儿时。父有重病。侍疾不离。至割股和药。自未十岁。诚孝已著闻。早弃科业。专意古人之学。杜门山野。沈潜玩索。自少至老。其身心动静。一循绳墨。居家。内外之别。长幼之序。奉先之礼。皆有定制。一以古人为法。与李珥自少为道义交。相与讲磨切磋。以至成德。其识见之高迈。才分之超绝。虽若不及于李珥。而至于操守之密。践履之笃。则李珥常自谓不及也。盖其涵养体认。功深力到。终日俨然。坐如泥塑。李珥言笑乐易。学者犹见其可亲。而成浑则学者虽同处十年。而愈见其可畏也。望之皆知其为成德君子也。赵宪之至行卓节。亦可为百世之师表。年辈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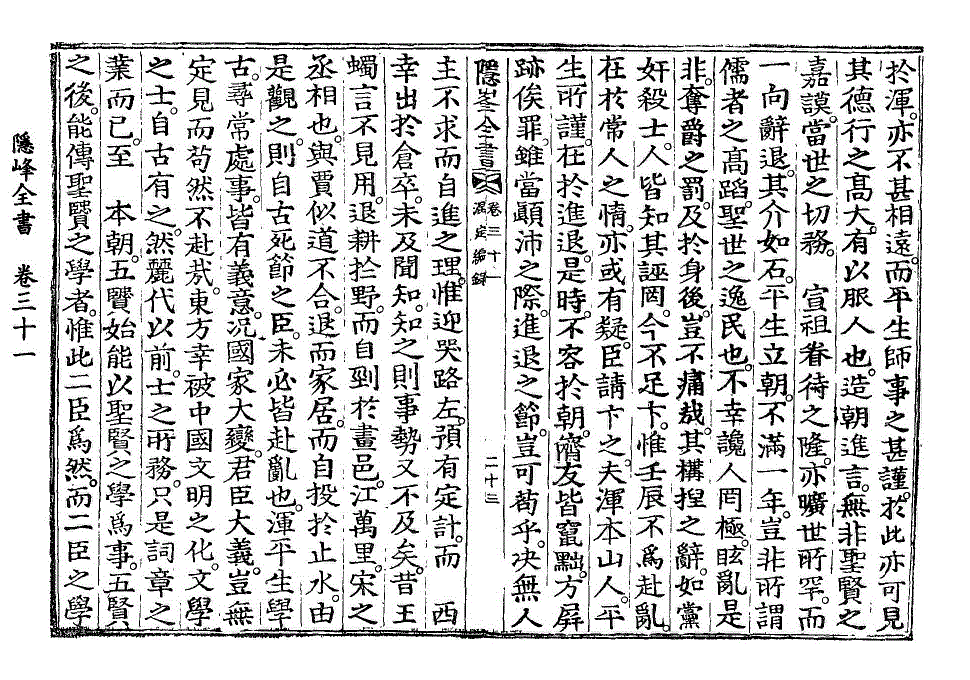 于浑。亦不甚相远。而平生师事之甚谨。于此亦可见其德行之高大。有以服人也。造朝进言。无非圣贤之嘉谟。当世之切务。 宣祖眷待之隆。亦旷世所罕。而一向辞退。其介如石。平生立朝。不满一年。岂非所谓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也。不幸谗人罔极。眩乱是非。夺爵之罚。及于身后。岂不痛哉。其构捏之辞。如党奸杀士。人皆知其诬罔。今不足卞。惟壬辰不为赴乱。在于常人之情。亦或有疑。臣请卞之。夫浑本山人。平生所谨。在于进退。是时。不容于朝。侪友皆窜黜。方屏迹俟罪。虽当颠沛之际。进退之节。岂可苟乎。决无人主不求而自进之理。惟迎哭路左。预有定计。而 西幸出于仓卒。未及闻知。知之则事势又不及矣。昔王蠋言不见用。退耕于野。而自刭于画邑。江万里。宋之丞相也。与贾似道不合。退而家居。而自投于止水。由是观之。则自古死节之臣。未必皆赴乱也。浑平生学古。寻常处事。皆有义意。况国家大变。君臣大义。岂无定见而苟然不赴哉。东方幸被中国文明之化。文学之士。自古有之。然丽代以前。士之所务。只是词章之业而已。至 本朝。五贤始能以圣贤之学为事。五贤之后。能传圣贤之学者。惟此二臣为然。而二臣之学
于浑。亦不甚相远。而平生师事之甚谨。于此亦可见其德行之高大。有以服人也。造朝进言。无非圣贤之嘉谟。当世之切务。 宣祖眷待之隆。亦旷世所罕。而一向辞退。其介如石。平生立朝。不满一年。岂非所谓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也。不幸谗人罔极。眩乱是非。夺爵之罚。及于身后。岂不痛哉。其构捏之辞。如党奸杀士。人皆知其诬罔。今不足卞。惟壬辰不为赴乱。在于常人之情。亦或有疑。臣请卞之。夫浑本山人。平生所谨。在于进退。是时。不容于朝。侪友皆窜黜。方屏迹俟罪。虽当颠沛之际。进退之节。岂可苟乎。决无人主不求而自进之理。惟迎哭路左。预有定计。而 西幸出于仓卒。未及闻知。知之则事势又不及矣。昔王蠋言不见用。退耕于野。而自刭于画邑。江万里。宋之丞相也。与贾似道不合。退而家居。而自投于止水。由是观之。则自古死节之臣。未必皆赴乱也。浑平生学古。寻常处事。皆有义意。况国家大变。君臣大义。岂无定见而苟然不赴哉。东方幸被中国文明之化。文学之士。自古有之。然丽代以前。士之所务。只是词章之业而已。至 本朝。五贤始能以圣贤之学为事。五贤之后。能传圣贤之学者。惟此二臣为然。而二臣之学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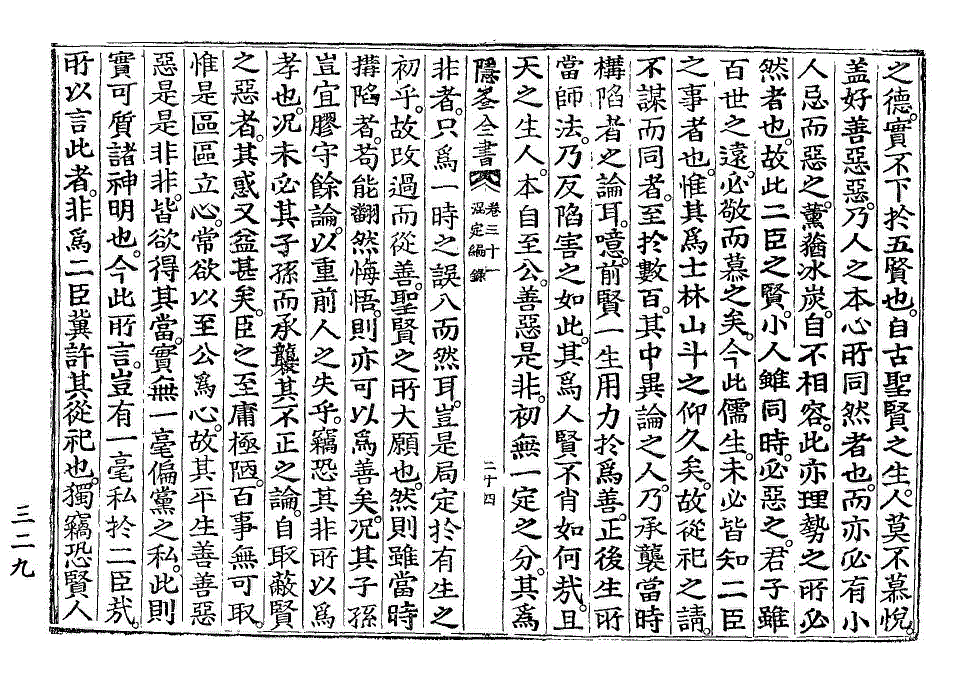 之德。实不下于五贤也。自古圣贤之生。人莫不慕悦。盖好善恶恶。乃人之本心所同然者也。而亦必有小人忌而恶之。薰莸冰炭。自不相容。此亦理势之所必然者也。故此二臣之贤。小人虽同时。必恶之。君子虽百世之远。必敬而慕之矣。今此儒生。未必皆知二臣之事者也。惟其为士林山斗之仰久矣。故从祀之请。不谋而同者。至于数百。其中异论之人。乃承袭当时构陷者之论耳。噫。前贤一生用力于为善。正后生所当师法。乃反陷害之如此。其为人贤不肖如何哉。且天之生人。本自至公。善恶是非。初无一定之分。其为非者。只为一时之误入而然耳。岂是局定于有生之初乎。故改过而从善。圣贤之所大愿也。然则虽当时搆陷者。苟能翻然悔悟。则亦可以为善矣。况其子孙岂宜胶守馀论。以重前人之失乎。窃恐其非所以为孝也。况未必其子孙而承袭其不正之论。自取蔽贤之恶者。其惑又益甚矣。臣之至庸极陋。百事无可取。惟是区区立心。常欲以至公为心。故其平生善善恶恶是是非非。皆欲得其当。实无一毫偏党之私。此则实可质诸神明也。今此所言。岂有一毫私于二臣哉。所以言此者。非为二臣冀许其从祀也。独窃恐贤人
之德。实不下于五贤也。自古圣贤之生。人莫不慕悦。盖好善恶恶。乃人之本心所同然者也。而亦必有小人忌而恶之。薰莸冰炭。自不相容。此亦理势之所必然者也。故此二臣之贤。小人虽同时。必恶之。君子虽百世之远。必敬而慕之矣。今此儒生。未必皆知二臣之事者也。惟其为士林山斗之仰久矣。故从祀之请。不谋而同者。至于数百。其中异论之人。乃承袭当时构陷者之论耳。噫。前贤一生用力于为善。正后生所当师法。乃反陷害之如此。其为人贤不肖如何哉。且天之生人。本自至公。善恶是非。初无一定之分。其为非者。只为一时之误入而然耳。岂是局定于有生之初乎。故改过而从善。圣贤之所大愿也。然则虽当时搆陷者。苟能翻然悔悟。则亦可以为善矣。况其子孙岂宜胶守馀论。以重前人之失乎。窃恐其非所以为孝也。况未必其子孙而承袭其不正之论。自取蔽贤之恶者。其惑又益甚矣。臣之至庸极陋。百事无可取。惟是区区立心。常欲以至公为心。故其平生善善恶恶是是非非。皆欲得其当。实无一毫偏党之私。此则实可质诸神明也。今此所言。岂有一毫私于二臣哉。所以言此者。非为二臣冀许其从祀也。独窃恐贤人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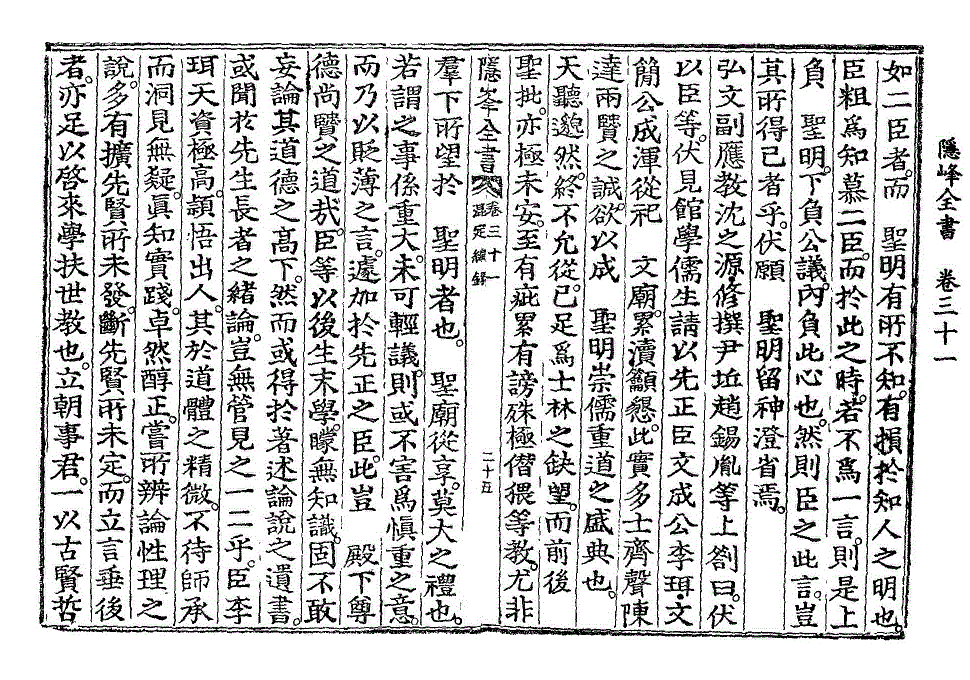 如二臣者。而 圣明有所不知。有损于知人之明也。臣粗为知慕二臣。而于此之时。若不为一言。则是上负 圣明。下负公议。内负此心也。然则臣之此言。岂其所得己者乎。伏愿 圣明留神澄省焉。
如二臣者。而 圣明有所不知。有损于知人之明也。臣粗为知慕二臣。而于此之时。若不为一言。则是上负 圣明。下负公议。内负此心也。然则臣之此言。岂其所得己者乎。伏愿 圣明留神澄省焉。弘文副应教沈之源,修撰尹丘赵锡胤等上劄曰。伏以臣等。伏见馆学儒生请以先正臣文成公李珥,文简公成浑从祀 文庙。累渎吁恳。此实多士齐声陈达两贤之诚。欲以成 圣明崇儒重道之盛典也。 天听邈然。终不允从。已足为士林之缺望。而前后 圣批。亦极未安。至有疵累有谤殊极僭猥等教。尤非群下所望于 圣明者也。 圣庙从享。莫大之礼也。若谓之事系重大。未可轻议。则或不害为慎重之意。而乃以贬薄之言。遽加于先正之臣。此岂 殿下尊德尚贤之道哉。臣等以后生末学。矇无知识。固不敢妄论其道德之高下。然而或得于著述论说之遗书。或闻于先生长者之绪论。岂无管见之一二乎。臣李珥天资极高。颖悟出人。其于道体之精微。不待师承而洞见无疑。真知实践。卓然醇正。尝所辨论性理之说。多有扩先贤所未发。断先贤所未定。而立言垂后者。亦足以启来学扶世教也。立朝事君。一以古贤哲
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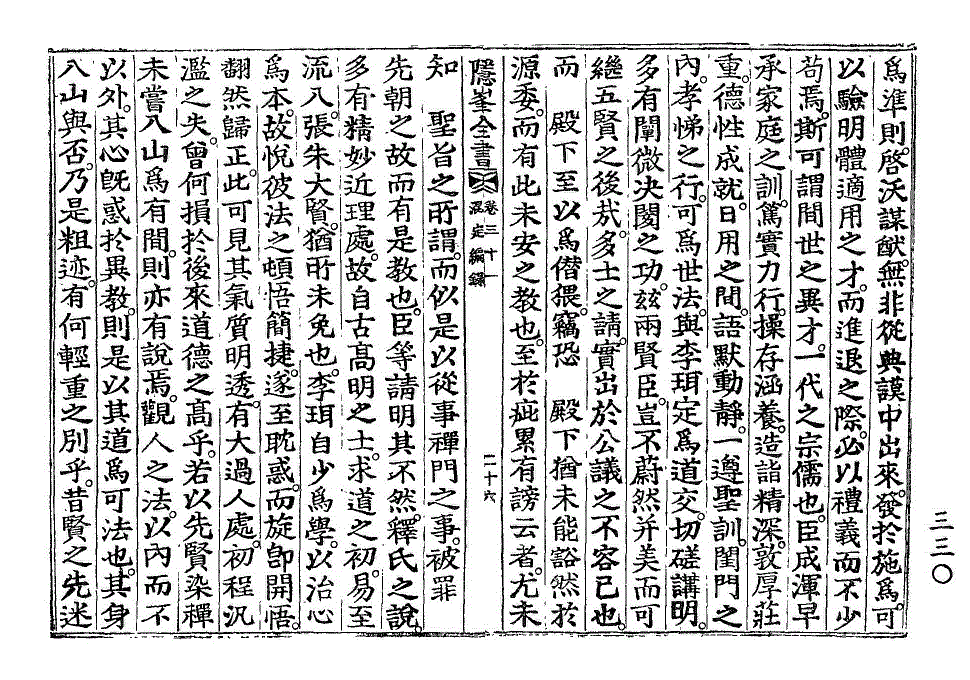 为准则。启沃谋猷。无非从典谟中出来。发于施为。可以验明体适用之才。而进退之际。必以礼义而不少苟焉。斯可谓间世之异才。一代之宗儒也。臣成浑早承家庭之训。笃实力行。操存涵养。造诣精深。敦厚庄重。德性成就。日用之间。语默动静。一遵圣训。闺门之内。孝悌之行。可为世法。与李珥定为道交。切磋讲明。多有阐微决阂之功。玆两贤臣。岂不蔚然并美而可继五贤之后哉。多士之请。实出于公议之不容己也。而 殿下至以为僭猥。窃恐 殿下犹未能豁然于源委。而有此未安之教也。至于疵累有谤云者。尤未知 圣旨之所谓。而似是以从事禅门之事。被罪 先朝之故而有是教也。臣等请明其不然。释氏之说。多有精妙近理处。故自古高明之士。求道之初。易至流入。张朱大贤。犹所未免也。李珥自少为学。以治心为本。故悦彼法之顿悟简捷。遂至耽惑。而旋即开悟。翻然归正。此可见其气质明透。有大过人处。初程汎滥之失。曾何损于后来道德之高乎。若以先贤染禅未尝入山为有间。则亦有说焉。观人之法。以内而不以外。其心既惑于异教。则是以其道为可法也。其身入山与否。乃是粗迹。有何轻重之别乎。昔贤之先迷
为准则。启沃谋猷。无非从典谟中出来。发于施为。可以验明体适用之才。而进退之际。必以礼义而不少苟焉。斯可谓间世之异才。一代之宗儒也。臣成浑早承家庭之训。笃实力行。操存涵养。造诣精深。敦厚庄重。德性成就。日用之间。语默动静。一遵圣训。闺门之内。孝悌之行。可为世法。与李珥定为道交。切磋讲明。多有阐微决阂之功。玆两贤臣。岂不蔚然并美而可继五贤之后哉。多士之请。实出于公议之不容己也。而 殿下至以为僭猥。窃恐 殿下犹未能豁然于源委。而有此未安之教也。至于疵累有谤云者。尤未知 圣旨之所谓。而似是以从事禅门之事。被罪 先朝之故而有是教也。臣等请明其不然。释氏之说。多有精妙近理处。故自古高明之士。求道之初。易至流入。张朱大贤。犹所未免也。李珥自少为学。以治心为本。故悦彼法之顿悟简捷。遂至耽惑。而旋即开悟。翻然归正。此可见其气质明透。有大过人处。初程汎滥之失。曾何损于后来道德之高乎。若以先贤染禅未尝入山为有间。则亦有说焉。观人之法。以内而不以外。其心既惑于异教。则是以其道为可法也。其身入山与否。乃是粗迹。有何轻重之别乎。昔贤之先迷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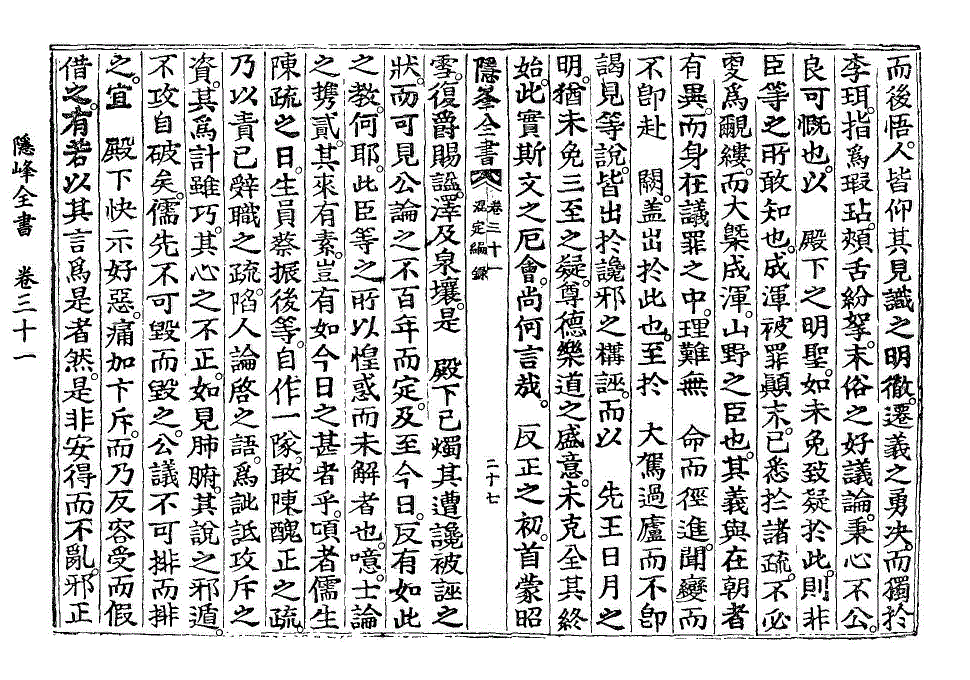 而后悟。人皆仰其见识之明彻。迁义之勇决。而独于李珥。指为瑕玷。颊舌纷挐。末俗之好议论。秉心不公。良可慨也。以 殿下之明圣。如未免致疑于此。则非臣等之所敢知也。成浑被罪颠末。已悉于诸疏。不必更为覼缕。而大槩成浑。山野之臣也。其义与在朝者有异。而身在议罪之中。理难无 命而径进。闻变而不即赴 阙。盖出于此也。至于 大驾过庐而不即谒见等说。皆出于谗邪之构诬。而以 先王日月之明。犹未免三至之疑。尊德乐道之盛意。未克全其终始。此实斯文之厄会。尚何言哉。 反正之初。首蒙昭雪。复爵赐谥。泽及泉壤。是 殿下已烛其遭谗被诬之状。而可见公论之不百年而定。及至今日。反有如此之教。何耶。此臣等之所以惶惑而未解者也。噫。士论之携贰。其来有素。岂有如今日之甚者乎。顷者儒生陈疏之日。生员蔡振后等。自作一队。敢陈丑正之疏。乃以责己辞职之疏。陷人论启之语。为訾诋攻斥之资。其为计虽巧。其心之不正。如见肺腑。其说之邪遁。不攻自破矣。儒先不可毁而毁之。公议不可排而排之。宜 殿下快示好恶。痛加卞斥。而乃反容受而假借之。有若以其言为是者然。是非安得而不乱。邪正
而后悟。人皆仰其见识之明彻。迁义之勇决。而独于李珥。指为瑕玷。颊舌纷挐。末俗之好议论。秉心不公。良可慨也。以 殿下之明圣。如未免致疑于此。则非臣等之所敢知也。成浑被罪颠末。已悉于诸疏。不必更为覼缕。而大槩成浑。山野之臣也。其义与在朝者有异。而身在议罪之中。理难无 命而径进。闻变而不即赴 阙。盖出于此也。至于 大驾过庐而不即谒见等说。皆出于谗邪之构诬。而以 先王日月之明。犹未免三至之疑。尊德乐道之盛意。未克全其终始。此实斯文之厄会。尚何言哉。 反正之初。首蒙昭雪。复爵赐谥。泽及泉壤。是 殿下已烛其遭谗被诬之状。而可见公论之不百年而定。及至今日。反有如此之教。何耶。此臣等之所以惶惑而未解者也。噫。士论之携贰。其来有素。岂有如今日之甚者乎。顷者儒生陈疏之日。生员蔡振后等。自作一队。敢陈丑正之疏。乃以责己辞职之疏。陷人论启之语。为訾诋攻斥之资。其为计虽巧。其心之不正。如见肺腑。其说之邪遁。不攻自破矣。儒先不可毁而毁之。公议不可排而排之。宜 殿下快示好恶。痛加卞斥。而乃反容受而假借之。有若以其言为是者然。是非安得而不乱。邪正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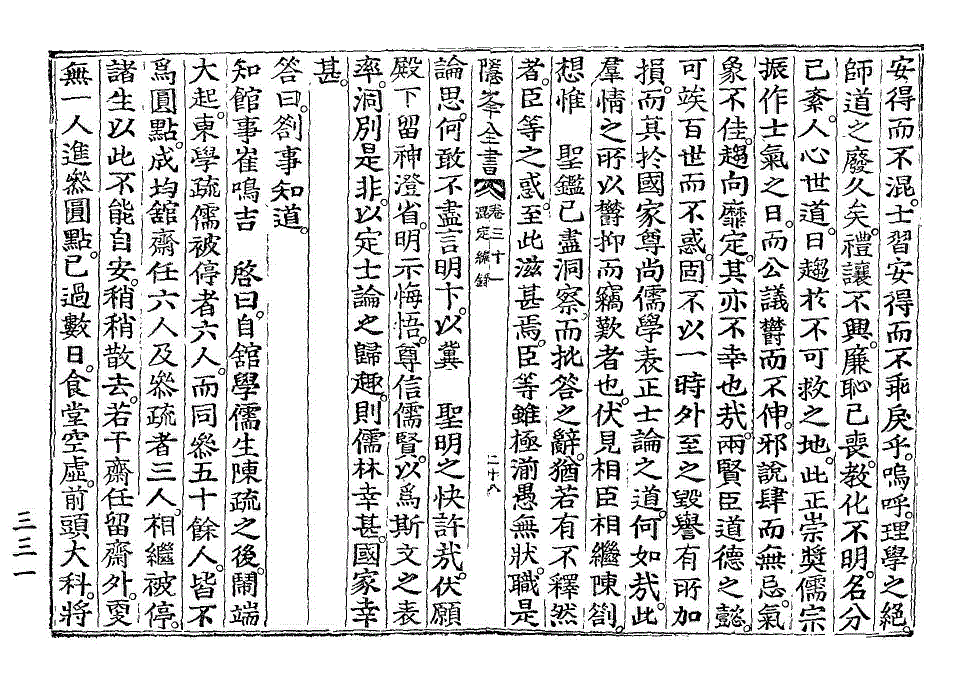 安得而不混。士习安得而不乖戾乎。呜呼。理学之绝。师道之废久矣。礼让不兴。廉耻已丧。教化不明。名分已紊。人心世道。日趋于不可救之地。此正崇奖儒宗振作士气之日。而公议郁而不伸。邪说肆而无忌。气象不佳。趋向靡定。其亦不幸也哉。两贤臣道德之懿。可俟百世而不惑。固不以一时外至之毁誉有所加损。而其于国家尊尚儒学表正士论之道。何如哉。此群情之所以郁抑而窃叹者也。伏见相臣相继陈劄。想惟 圣鉴已尽洞察。而批答之辞。犹若有不释然者。臣等之惑。至此滋甚焉。臣等虽极湔愚无状。职是论思。何敢不尽言明下。以冀 圣明之快许哉。伏愿殿下留神澄省。明示悔悟。尊信儒贤。以为斯文之表率。洞别是非。以定士论之归趣。则儒林幸甚。国家幸甚。
安得而不混。士习安得而不乖戾乎。呜呼。理学之绝。师道之废久矣。礼让不兴。廉耻已丧。教化不明。名分已紊。人心世道。日趋于不可救之地。此正崇奖儒宗振作士气之日。而公议郁而不伸。邪说肆而无忌。气象不佳。趋向靡定。其亦不幸也哉。两贤臣道德之懿。可俟百世而不惑。固不以一时外至之毁誉有所加损。而其于国家尊尚儒学表正士论之道。何如哉。此群情之所以郁抑而窃叹者也。伏见相臣相继陈劄。想惟 圣鉴已尽洞察。而批答之辞。犹若有不释然者。臣等之惑。至此滋甚焉。臣等虽极湔愚无状。职是论思。何敢不尽言明下。以冀 圣明之快许哉。伏愿殿下留神澄省。明示悔悟。尊信儒贤。以为斯文之表率。洞别是非。以定士论之归趣。则儒林幸甚。国家幸甚。答曰。劄事知道。
知馆事崔鸣吉 启曰。自馆学儒生陈疏之后。闹端大起。东学疏儒被停者六人。而同参五十馀人。皆不为圆点。成均馆斋任六人及参疏者三人。相继被停。诸生以此不能自安。稍稍散去。若干斋任留斋外。更无一人进参圆点。已过数日。食堂空虚。前头大科。将
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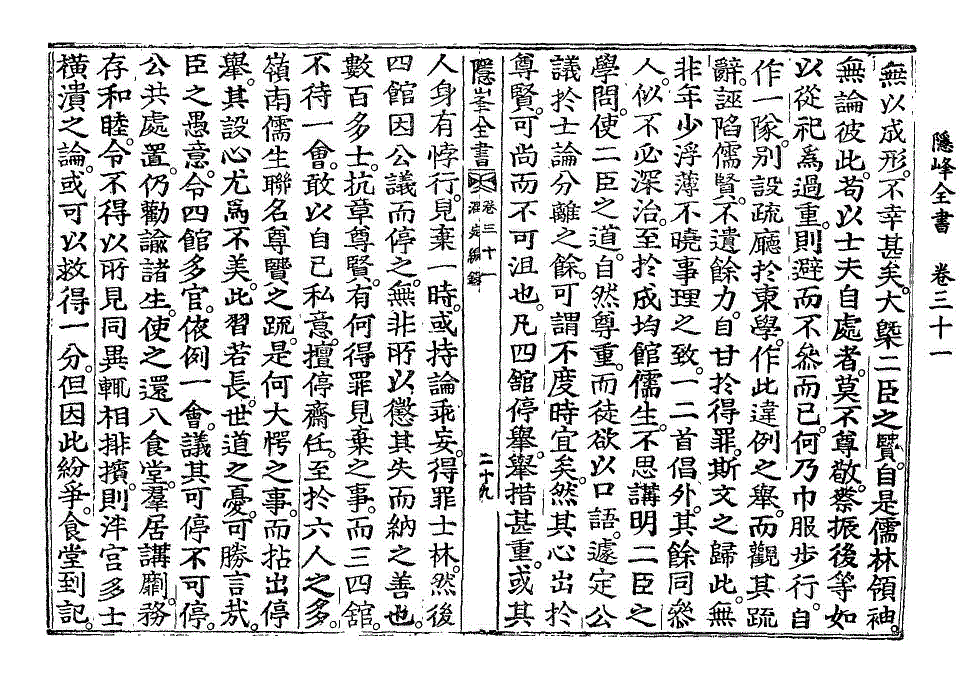 无以成形。不幸甚矣。大槩二臣之贤。自是儒林领袖。无论彼此。苟以士夫自处者。莫不尊敬。蔡振后等如以从祀为过重。则避而不参而已。何乃巾服步行。自作一队。别设疏厅于东学。作此违例之举。而观其疏辞。诬陷儒贤。不遗馀力。自甘于得罪。斯文之归此。无非年少浮薄不晓事理之致。一二首倡外。其馀同参人。似不必深治。至于成均馆儒生。不思讲明二臣之学问。使二臣之道。自然尊重。而徒欲以口语。遽定公议于士论分离之馀。可谓不度时宜矣。然其心出于尊贤。可尚而不可沮也。凡四馆停举。举措甚重。或其人身有悖行。见弃一时。或持论乖妄。得罪士林。然后四馆因公议而停之。无非所以惩其失而纳之善也。数百多士。抗章尊贤。有何得罪见弃之事。而三四馆。不待一会。敢以自己私意。擅停斋任。至于六人之多。岭南儒生联名尊贤之疏。是何大愕之事。而拈出停举。其设心尤为不美。此习若长。世道之忧。可胜言哉。臣之愚意。令四馆多官。依例一会。议其可停不可停。公共处置。仍劝谕诸生。使之还入食堂。群居讲劘。务存和睦。令不得以所见同异辄相排摈。则泮宫多士横溃之论。或可以救得一分。但因此纷争。食堂到记。
无以成形。不幸甚矣。大槩二臣之贤。自是儒林领袖。无论彼此。苟以士夫自处者。莫不尊敬。蔡振后等如以从祀为过重。则避而不参而已。何乃巾服步行。自作一队。别设疏厅于东学。作此违例之举。而观其疏辞。诬陷儒贤。不遗馀力。自甘于得罪。斯文之归此。无非年少浮薄不晓事理之致。一二首倡外。其馀同参人。似不必深治。至于成均馆儒生。不思讲明二臣之学问。使二臣之道。自然尊重。而徒欲以口语。遽定公议于士论分离之馀。可谓不度时宜矣。然其心出于尊贤。可尚而不可沮也。凡四馆停举。举措甚重。或其人身有悖行。见弃一时。或持论乖妄。得罪士林。然后四馆因公议而停之。无非所以惩其失而纳之善也。数百多士。抗章尊贤。有何得罪见弃之事。而三四馆。不待一会。敢以自己私意。擅停斋任。至于六人之多。岭南儒生联名尊贤之疏。是何大愕之事。而拈出停举。其设心尤为不美。此习若长。世道之忧。可胜言哉。臣之愚意。令四馆多官。依例一会。议其可停不可停。公共处置。仍劝谕诸生。使之还入食堂。群居讲劘。务存和睦。令不得以所见同异辄相排摈。则泮宫多士横溃之论。或可以救得一分。但因此纷争。食堂到记。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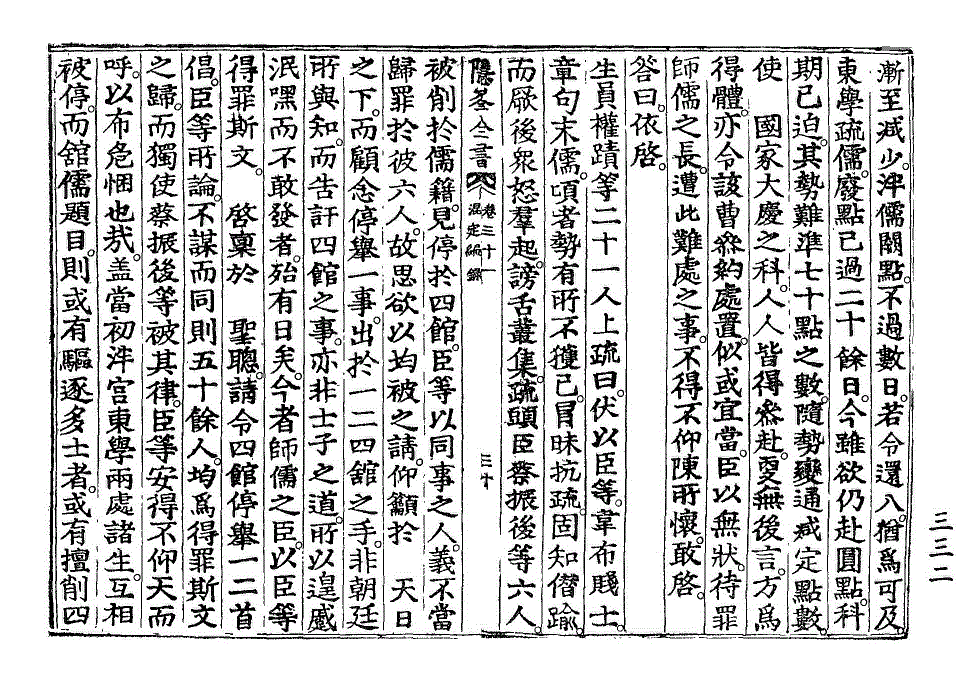 渐至减少。泮儒阙点。不过数日。若令还入。犹为可及。东学疏儒。废点已过二十馀日。今虽欲仍赴圆点。科期已迫。其势难准七十点之数。随势变通减定点数。使 国家大庆之科。人人皆得参赴。更无后言。方为得体。亦令该曹参约处置。似或宜当。臣以无状。待罪师儒之长。遭此难处之事。不得不仰陈所怀。敢启。
渐至减少。泮儒阙点。不过数日。若令还入。犹为可及。东学疏儒。废点已过二十馀日。今虽欲仍赴圆点。科期已迫。其势难准七十点之数。随势变通减定点数。使 国家大庆之科。人人皆得参赴。更无后言。方为得体。亦令该曹参约处置。似或宜当。臣以无状。待罪师儒之长。遭此难处之事。不得不仰陈所怀。敢启。答曰。依启。
生员权迹等二十一人上疏曰。伏以臣等。韦布贱士。章句末儒。顷者势有所不获已。冒昧抗疏。固知僭踰。而厥后众怒群起。谤舌丛集。疏头臣蔡振后等六人。被削于儒籍。见停于四馆。臣等以同事之人。义不当归罪于彼六人。故思欲以均被之情。仰吁于 天日之下。而顾念停举一事。出于一二四馆之手。非朝廷所与知。而告讦四馆之事。亦非士子之道。所以遑蹙泯默而不敢发者。殆有日矣。今者师儒之臣。以臣等得罪斯文。 启禀于 圣聪。请令四馆停举一二首倡。臣等所论。不谋而同则五十馀人。均为得罪斯文之归。而独使蔡振后等被其律。臣等安得不仰天而呼。以布危悃也哉。盖当初泮宫东学两处诸生。互相被停。而馆儒题目。则或有驱逐多士者。或有擅削四
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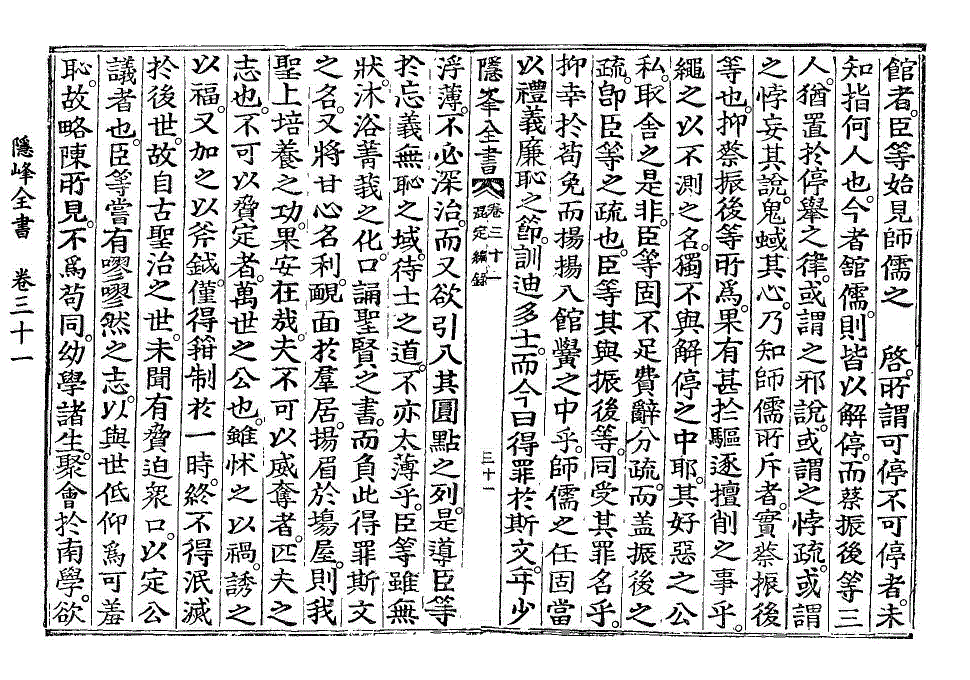 馆者。臣等始见师儒之 启。所谓可停不可停者。未知指何人也。今者馆儒。则皆以解停。而蔡振后等三人。犹置于停举之律。或谓之邪说。或谓之悖疏。或谓之悖妄其说。鬼蜮其心。乃知师儒所斥者。实蔡振后等也。抑蔡振后等所为。果有甚于驱逐擅削之事乎。绳之以不测之名。独不与解停之中耶。其好恶之公私。取舍之是非。臣等固不足费辞分疏。而盖振后之疏。即臣等之疏也。臣等其与振后等。同受其罪名乎。抑幸于苟免而扬扬入馆黉之中乎。师儒之任固当以礼义廉耻之节。训迪多士。而今曰得罪于斯文。年少浮薄。不必深治。而又欲引入其圆点之列。是导臣等于忘义无耻之域。待士之道。不亦太薄乎。臣等虽无状。沐浴菁莪之化。口诵圣贤之书。而负此得罪斯文之名。又将甘心名利。腼面于群居。扬眉于场屋。则我圣上培养之功。果安在哉。夫不可以威夺者。匹夫之志也。不可以胁定者。万世之公也。虽怵之以祸。诱之以福。又加之以斧钺。仅得钳制于一时。终不得泯灭于后世。故自古圣治之世。未闻有胁迫众口。以定公议者也。臣等尝有嘐嘐然之志。以与世低仰为可羞耻。故略陈所见。不为苟同。幼学诸生。聚会于南学。欲
馆者。臣等始见师儒之 启。所谓可停不可停者。未知指何人也。今者馆儒。则皆以解停。而蔡振后等三人。犹置于停举之律。或谓之邪说。或谓之悖疏。或谓之悖妄其说。鬼蜮其心。乃知师儒所斥者。实蔡振后等也。抑蔡振后等所为。果有甚于驱逐擅削之事乎。绳之以不测之名。独不与解停之中耶。其好恶之公私。取舍之是非。臣等固不足费辞分疏。而盖振后之疏。即臣等之疏也。臣等其与振后等。同受其罪名乎。抑幸于苟免而扬扬入馆黉之中乎。师儒之任固当以礼义廉耻之节。训迪多士。而今曰得罪于斯文。年少浮薄。不必深治。而又欲引入其圆点之列。是导臣等于忘义无耻之域。待士之道。不亦太薄乎。臣等虽无状。沐浴菁莪之化。口诵圣贤之书。而负此得罪斯文之名。又将甘心名利。腼面于群居。扬眉于场屋。则我圣上培养之功。果安在哉。夫不可以威夺者。匹夫之志也。不可以胁定者。万世之公也。虽怵之以祸。诱之以福。又加之以斧钺。仅得钳制于一时。终不得泯灭于后世。故自古圣治之世。未闻有胁迫众口。以定公议者也。臣等尝有嘐嘐然之志。以与世低仰为可羞耻。故略陈所见。不为苟同。幼学诸生。聚会于南学。欲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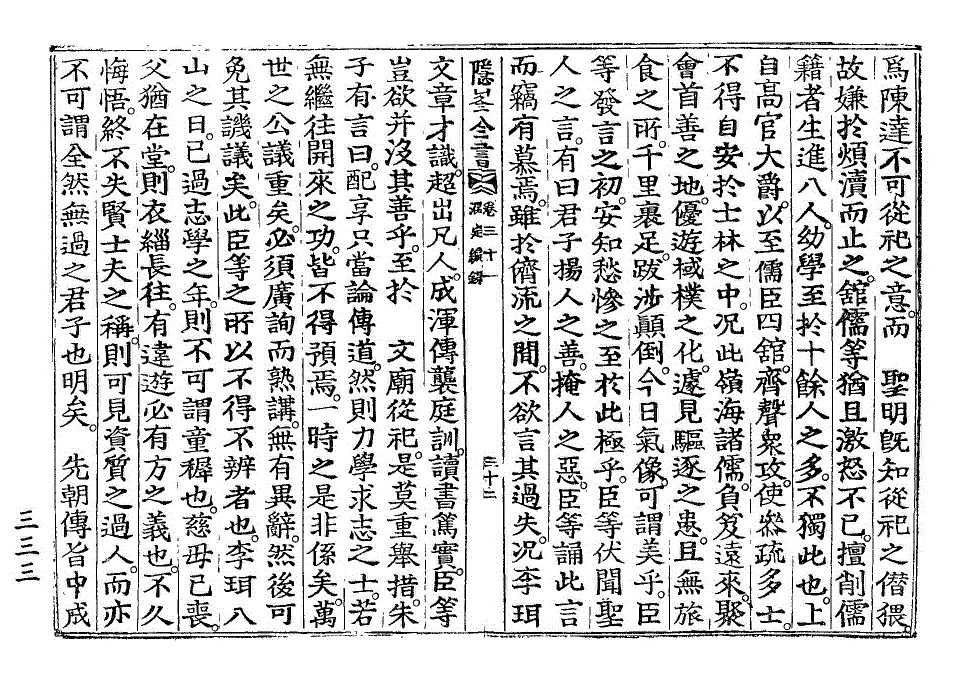 为陈达不可从祀之意。而 圣明既知从祀之僭猥。故嫌于烦渎而止之。馆儒等犹且激怒不已。擅削儒籍者生进八人。幼学至于十馀人之多。不独此也。上自高官大爵。以至儒臣四馆。齐声众攻。使参疏多士。不得自安于士林之中。况此岭海诸儒。负笈远来。聚会首善之地。优游棫朴之化。遽见驱逐之患。且无旅食之所。千里裹足。跋涉颠倒。今日气像。可谓美乎。臣等发言之初。安知愁惨之至于此极乎。臣等伏闻圣人之言。有曰君子扬人之善。掩人之恶。臣等诵此言而窃有慕焉。虽于侪流之间。不欲言其过失。况李珥文章才识。超出凡人。成浑传袭庭训。读书笃实。臣等岂欲并没其善乎。至于 文庙从祀。是莫重举措。朱子有言曰。配享只当论传道。然则力学求志之士。若无继往开来之功。皆不得预焉。一时之是非系矣。万世之公议重矣。必须广询而熟讲。无有异辞。然后可免其讥议矣。此臣等之所以不得不辨者也。李珥入山之日。已过志学之年。则不可谓童稚也。慈母已丧。父犹在堂。则衣缁长往。有违游必有方之义也。不久悔悟。终不失贤士夫之称。则可见资质之过人。而亦不可谓全然无过之君子也明矣。 先朝传旨中成
为陈达不可从祀之意。而 圣明既知从祀之僭猥。故嫌于烦渎而止之。馆儒等犹且激怒不已。擅削儒籍者生进八人。幼学至于十馀人之多。不独此也。上自高官大爵。以至儒臣四馆。齐声众攻。使参疏多士。不得自安于士林之中。况此岭海诸儒。负笈远来。聚会首善之地。优游棫朴之化。遽见驱逐之患。且无旅食之所。千里裹足。跋涉颠倒。今日气像。可谓美乎。臣等发言之初。安知愁惨之至于此极乎。臣等伏闻圣人之言。有曰君子扬人之善。掩人之恶。臣等诵此言而窃有慕焉。虽于侪流之间。不欲言其过失。况李珥文章才识。超出凡人。成浑传袭庭训。读书笃实。臣等岂欲并没其善乎。至于 文庙从祀。是莫重举措。朱子有言曰。配享只当论传道。然则力学求志之士。若无继往开来之功。皆不得预焉。一时之是非系矣。万世之公议重矣。必须广询而熟讲。无有异辞。然后可免其讥议矣。此臣等之所以不得不辨者也。李珥入山之日。已过志学之年。则不可谓童稚也。慈母已丧。父犹在堂。则衣缁长往。有违游必有方之义也。不久悔悟。终不失贤士夫之称。则可见资质之过人。而亦不可谓全然无过之君子也明矣。 先朝传旨中成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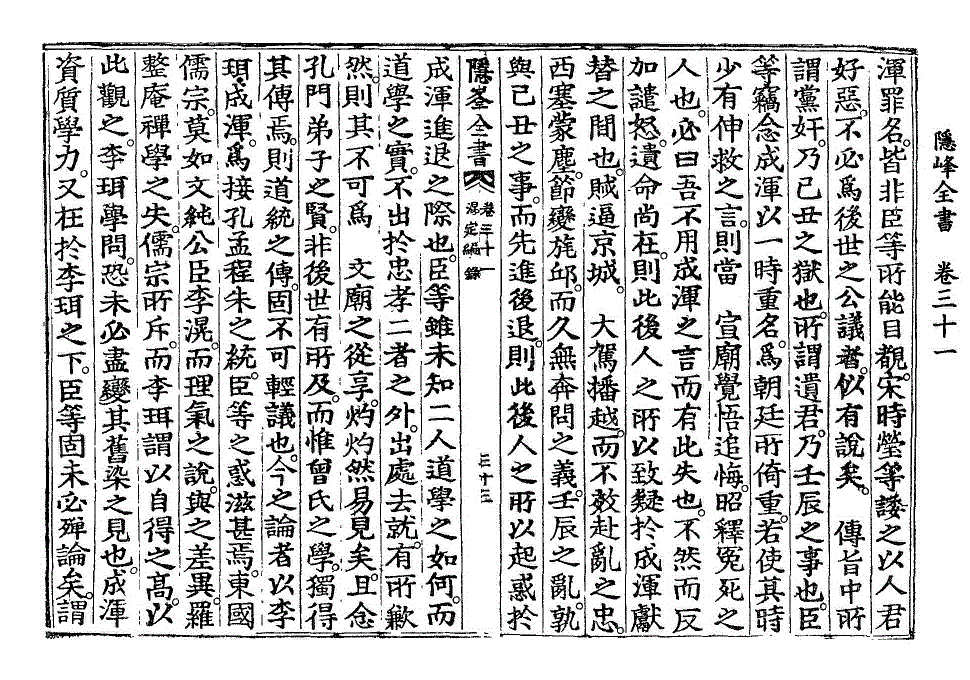 浑罪召。皆非臣等所能目睹。宋时莹等诿之以人君好恶。不必为后世之公议者。似有说矣。 传旨中所谓党奸。乃己丑之狱也。所谓遗君。乃壬辰之事也。臣等窃念成浑以一时重名。为朝廷所倚重。若使其时少有伸救之言。则当 宣庙觉悟追悔。昭释冤死之人也。必曰吾不用成浑之言而有此失也。不然而反加谴怒。遗命尚在。则此后人之所以致疑于成浑献替之间也。贼逼京城。 大驾播越。而不效赴乱之忠。西塞蒙尘。节变旄邱。而久无奔问之义。壬辰之乱。孰与己丑之事。而先进后退。则此后人之所以起惑于成浑进退之际也。臣等虽未知二人道学之如何。而道学之实。不出于忠孝二者之外。出处去就。有所歉然。则其不可为 文庙之从享。灼灼然易见矣。且念孔门弟子之贤。非后世有所及。而惟曾氏之学。独得其传焉。则道统之传。固不可经议也。今之论者以李珥,成浑。为接孔孟程朱之统。臣等之惑滋甚焉。东国儒宗。莫如文纯公臣李滉。而理气之说。与之差异。罗整庵禅学之失。儒宗所斥。而李珥谓以自得之高。以此观之。李珥学问。恐未必尽变其旧染之见也。成浑资质学力。又在于李珥之下。臣等固未必殚论矣。谓
浑罪召。皆非臣等所能目睹。宋时莹等诿之以人君好恶。不必为后世之公议者。似有说矣。 传旨中所谓党奸。乃己丑之狱也。所谓遗君。乃壬辰之事也。臣等窃念成浑以一时重名。为朝廷所倚重。若使其时少有伸救之言。则当 宣庙觉悟追悔。昭释冤死之人也。必曰吾不用成浑之言而有此失也。不然而反加谴怒。遗命尚在。则此后人之所以致疑于成浑献替之间也。贼逼京城。 大驾播越。而不效赴乱之忠。西塞蒙尘。节变旄邱。而久无奔问之义。壬辰之乱。孰与己丑之事。而先进后退。则此后人之所以起惑于成浑进退之际也。臣等虽未知二人道学之如何。而道学之实。不出于忠孝二者之外。出处去就。有所歉然。则其不可为 文庙之从享。灼灼然易见矣。且念孔门弟子之贤。非后世有所及。而惟曾氏之学。独得其传焉。则道统之传。固不可经议也。今之论者以李珥,成浑。为接孔孟程朱之统。臣等之惑滋甚焉。东国儒宗。莫如文纯公臣李滉。而理气之说。与之差异。罗整庵禅学之失。儒宗所斥。而李珥谓以自得之高。以此观之。李珥学问。恐未必尽变其旧染之见也。成浑资质学力。又在于李珥之下。臣等固未必殚论矣。谓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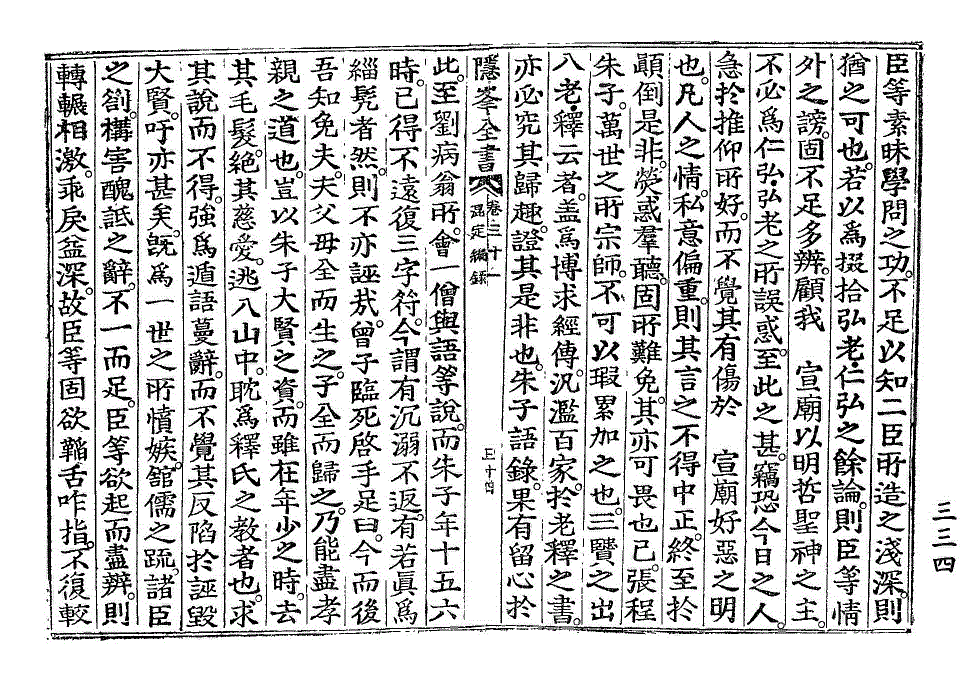 臣等素昧学问之功。不足以知二臣所造之浅深。则犹之可也。若以为掇拾弘老,仁弘之馀论。则臣等情外之谤。固不足多辨。顾我 宣庙以明哲圣神之主。不必为仁弘,弘老之所误惑。至此之甚。窃恐今日之人。急于推仰所好。而不觉其有伤于 宣庙好恶之明也。凡人之情。私意偏重。则其言之不得中正。终至于颠倒是非。荧惑群听。固所难免。其亦可畏也已。张程朱子。万世之所宗师。不可以瑕累加之也。三贤之出八老,释云者。盖为博求经传。汎滥百家。于老释之书。亦必究其归趣。證其是非也。朱子语录。果有留心于此。至刘病翁所。会一僧与语等说。而朱子年十五六时。已得不远复三字符。今谓有沈溺不返。有若真为缁髡者然。则不亦诬哉。曾子临死启手足曰。今而后吾知免夫。夫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乃能尽孝亲之道也。岂以朱子大贤之资。而虽在年少之时。去其毛发。绝其慈爱。逃入山中。耽为释氏之教者也。求其说而不得。强为遁语蔓辞。而不觉其反陷于诬毁大贤。吁亦甚矣。既为一世之所愤嫉。馆儒之疏。诸臣之劄。构害丑诋之辞。不一而足。臣等欲起而尽辨。则转辗相激。乖戾益深。故臣等固欲韬舌咋指。不复较
臣等素昧学问之功。不足以知二臣所造之浅深。则犹之可也。若以为掇拾弘老,仁弘之馀论。则臣等情外之谤。固不足多辨。顾我 宣庙以明哲圣神之主。不必为仁弘,弘老之所误惑。至此之甚。窃恐今日之人。急于推仰所好。而不觉其有伤于 宣庙好恶之明也。凡人之情。私意偏重。则其言之不得中正。终至于颠倒是非。荧惑群听。固所难免。其亦可畏也已。张程朱子。万世之所宗师。不可以瑕累加之也。三贤之出八老,释云者。盖为博求经传。汎滥百家。于老释之书。亦必究其归趣。證其是非也。朱子语录。果有留心于此。至刘病翁所。会一僧与语等说。而朱子年十五六时。已得不远复三字符。今谓有沈溺不返。有若真为缁髡者然。则不亦诬哉。曾子临死启手足曰。今而后吾知免夫。夫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乃能尽孝亲之道也。岂以朱子大贤之资。而虽在年少之时。去其毛发。绝其慈爱。逃入山中。耽为释氏之教者也。求其说而不得。强为遁语蔓辞。而不觉其反陷于诬毁大贤。吁亦甚矣。既为一世之所愤嫉。馆儒之疏。诸臣之劄。构害丑诋之辞。不一而足。臣等欲起而尽辨。则转辗相激。乖戾益深。故臣等固欲韬舌咋指。不复较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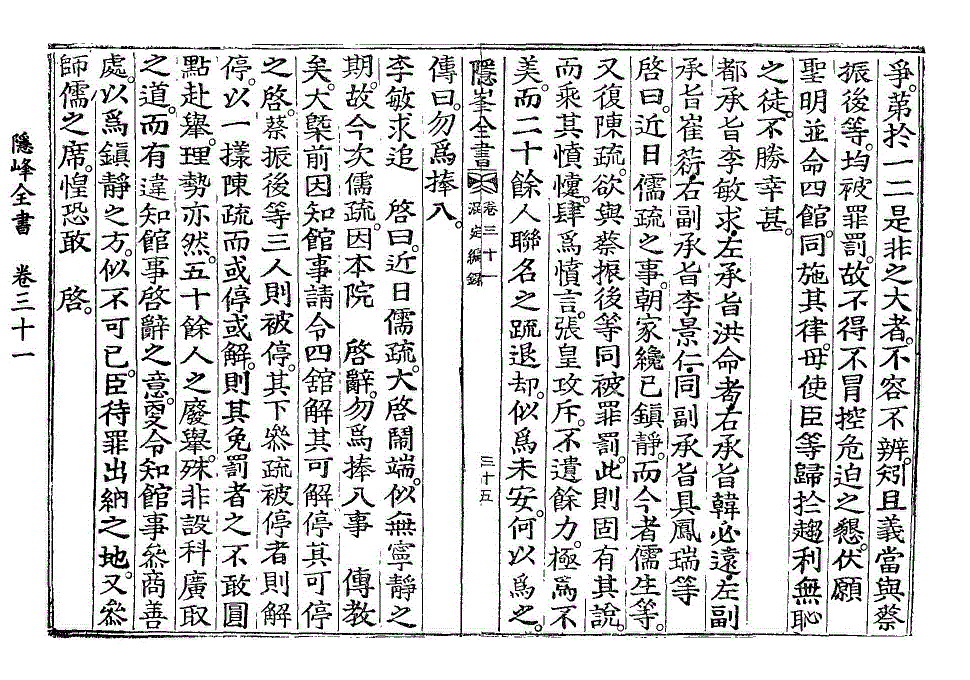 争。第于一二是非之大者。不容不辨。矧且义当与蔡振后等。均被罪罚。故不得不冒控危迫之恳。伏愿 圣明并命四馆。同施其律。毋使臣等归于趋利无耻之徒。不胜幸甚。
争。第于一二是非之大者。不容不辨。矧且义当与蔡振后等。均被罪罚。故不得不冒控危迫之恳。伏愿 圣明并命四馆。同施其律。毋使臣等归于趋利无耻之徒。不胜幸甚。都承旨李敏求,左承旨洪命耇,右承旨韩必远,左副承旨崔莚,右副承旨李景仁,同副承旨具凤瑞等 启曰。近日儒疏之事。朝家才已镇静。而今者儒生等。又复陈疏。欲与蔡振后等同被罪罚。此则固有其说。而乘其愤懥。肆为愤言。张皇攻斥。不遗馀力。极为不美。而二十馀人联名之疏退却。似为未安。何以为之。传曰。勿为捧入。
李敏求追 启曰。近日儒疏。大启闹端。似无宁静之期。故今次儒疏。因本院 启辞。勿为捧入事 传教矣。大槩前因知馆事请令四馆解其可解停其可停之启。蔡振后等三人则被停。其下参疏被停者则解停。以一样陈疏而或停或解。则其免罚者之不敢圆点赴举。理势亦然。五十馀人之废举。殊非设科广取之道。而有违知馆事启辞之意。更令知馆事参商善处以为镇静之方。似不可已。臣待罪出纳之地。又参师儒之席。惶恐敢 启。
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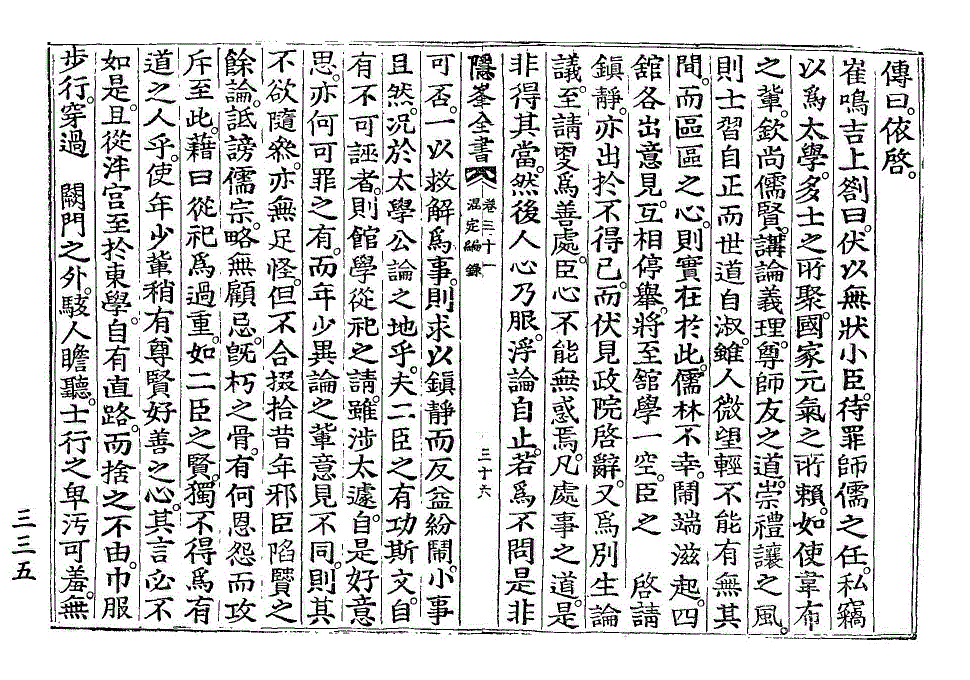 传曰。依启。
传曰。依启。崔鸣吉上劄曰。伏以无状小臣。待罪师儒之任。私窃以为太学。多士之所聚。国家元气之所赖。如使韦布之辈。钦尚儒贤。讲论义理。尊师友之道。崇礼让之风。则士习自正而世道自淑。虽人微望轻不能有无其间。而区区之心。则实在于此。儒林不幸。闹端滋起。四馆各出意见。互相停举。将至馆学一空。臣之 启请镇静。亦出于不得已。而伏见政院启辞。又为别生论议。至请更为善处。臣心不能无惑焉。凡处事之道。是非得其当。然后人心乃服。浮论自止。若为不问是非可否。一以救解为事。则求以镇静而反益纷闹。小事且然。况于太学公论之地乎。夫二臣之有功斯文。自有不可诬者。则馆学从祀之请。虽涉太遽。自是好意思。亦何可罪之有。而年少异论之辈意见不同。则其不欲随参。亦无足怪。但不合掇拾昔年邪臣陷贤之馀论。诋谤儒宗。略无顾忌。既朽之骨。有何恩怨而攻斥至此。藉曰从祀为过重。如二臣之贤。独不得为有道之人乎。使年少辈稍有尊贤好善之心。其言必不如是。且从泮宫至于东学。自有直路。而舍之不由。巾服步行。穿过 阙门之外。骇人瞻听。士行之卑污可羞。无
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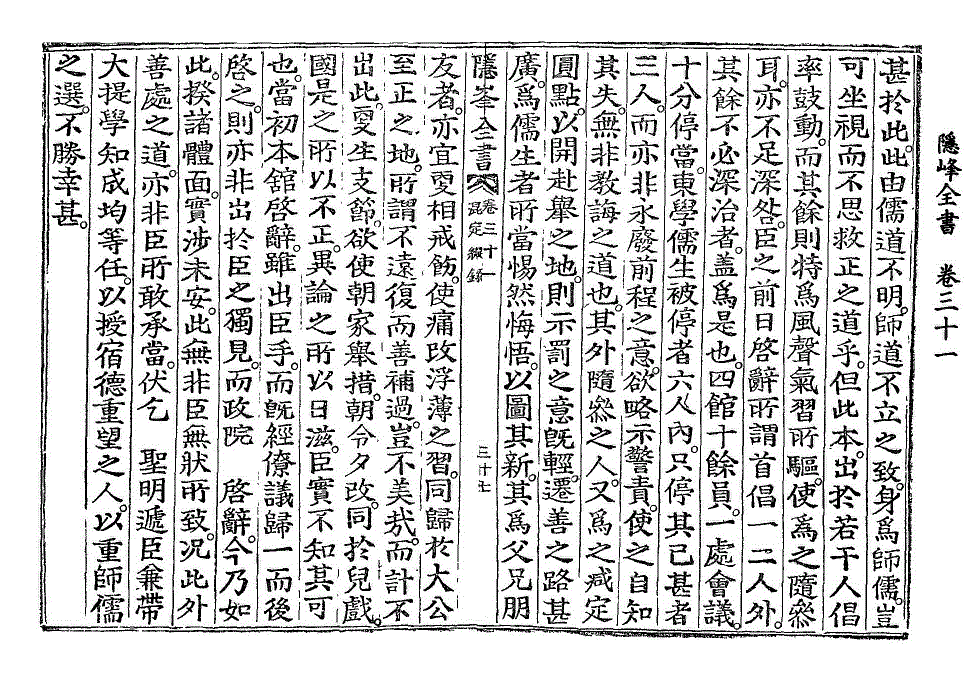 甚于此。此由儒道不明。师道不立之致。身为师儒。岂可坐视而不思救正之道乎。但此本。出于若干人倡率鼓动。而其馀则特为风声气习所驱。使为之随参耳。亦不足深咎。臣之前日启辞所谓首倡一二人外。其馀不必深治者。盖为是也。四馆十馀员。一处会议。十分停当。东学儒生被停者六人内。只停其已甚者三人。而亦非永废前程之意。欲略示警责。使之自知其失。无非教诲之道也。其外随参之人。又为之减定圆点。以开赴举之地。则示罚之意既轻。迁善之路甚广。为儒生者所当惕然悔悟。以图其新。其为父兄朋友者。亦宜更相戒饬。使痛改浮薄之习。同归于大公至正之地。所谓不远复而善补过。岂不美哉。而计不出此。更生支节。欲使朝家举措。朝令夕改。同于儿戏。国是之所以不正。异论之所以日滋。臣实不知其可也。当初本馆启辞。虽出臣手。而既经僚议归一而后启之。则亦非出于臣之独见。而政院 启辞。今乃如此。揆诸体面。实涉未安。此无非臣无状所致。况此外善处之道。亦非臣所敢承当。伏乞 圣明递臣兼带大提学知成均等任。以授宿德重望之人。以重师儒之选。不胜幸甚。
甚于此。此由儒道不明。师道不立之致。身为师儒。岂可坐视而不思救正之道乎。但此本。出于若干人倡率鼓动。而其馀则特为风声气习所驱。使为之随参耳。亦不足深咎。臣之前日启辞所谓首倡一二人外。其馀不必深治者。盖为是也。四馆十馀员。一处会议。十分停当。东学儒生被停者六人内。只停其已甚者三人。而亦非永废前程之意。欲略示警责。使之自知其失。无非教诲之道也。其外随参之人。又为之减定圆点。以开赴举之地。则示罚之意既轻。迁善之路甚广。为儒生者所当惕然悔悟。以图其新。其为父兄朋友者。亦宜更相戒饬。使痛改浮薄之习。同归于大公至正之地。所谓不远复而善补过。岂不美哉。而计不出此。更生支节。欲使朝家举措。朝令夕改。同于儿戏。国是之所以不正。异论之所以日滋。臣实不知其可也。当初本馆启辞。虽出臣手。而既经僚议归一而后启之。则亦非出于臣之独见。而政院 启辞。今乃如此。揆诸体面。实涉未安。此无非臣无状所致。况此外善处之道。亦非臣所敢承当。伏乞 圣明递臣兼带大提学知成均等任。以授宿德重望之人。以重师儒之选。不胜幸甚。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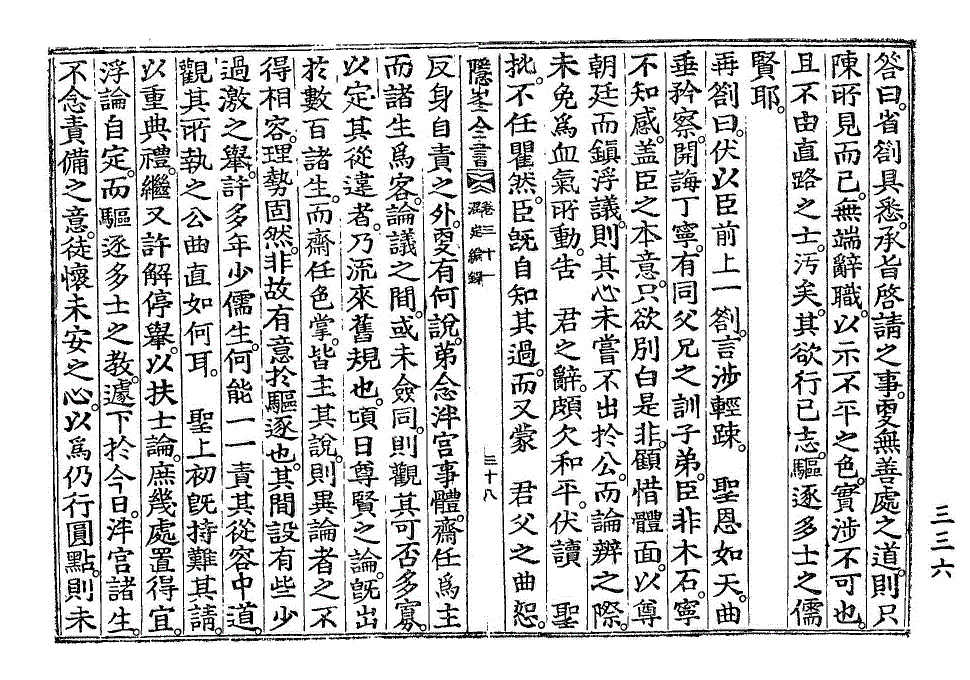 答曰。省劄具悉。承旨启请之事。更无善处之道。则只陈所见而已。无端辞职。以示不平之色。实涉不可也。且不由直路之士。污矣。其欲行己志。驱逐多士之儒贤耶。
答曰。省劄具悉。承旨启请之事。更无善处之道。则只陈所见而已。无端辞职。以示不平之色。实涉不可也。且不由直路之士。污矣。其欲行己志。驱逐多士之儒贤耶。再劄曰。伏以臣前上一劄。言涉轻疏。 圣恩如天。曲垂矜察。开诲丁宁。有同父兄之训子弟。臣非木石。宁不知感。盖臣之本意。只欲别白是非。顾惜体面。以尊朝廷而镇浮议。则其心未尝不出于公。而论辨之际。未免为血气所动。告 君之辞。颇欠和平。伏读 圣批。不任瞿然。臣既自知其过。而又蒙 君父之曲恕。反身自责之外。更有何说。第念泮官事体。斋任为主而诸生为客。论议之间。或未佥同。则观其可否多寡。以定其从违者。乃流来旧规也。顷日尊贤之论。既出于数百诸生。而斋任色掌。皆主其说。则异论者之不得相容。理势固然。非故有意于驱逐也。其间设有些少过激之举。许多年少儒生。何能一一责其从容中道。观其所执之公曲直如何耳。 圣上初既持难其请。以重典礼。继又许解停举。以扶士论。庶几处置得宜。浮论自定。而驱逐多士之教。遽下于今日。泮宫诸生。不念责备之意。徒怀未安之心。以为仍行圆点。则未
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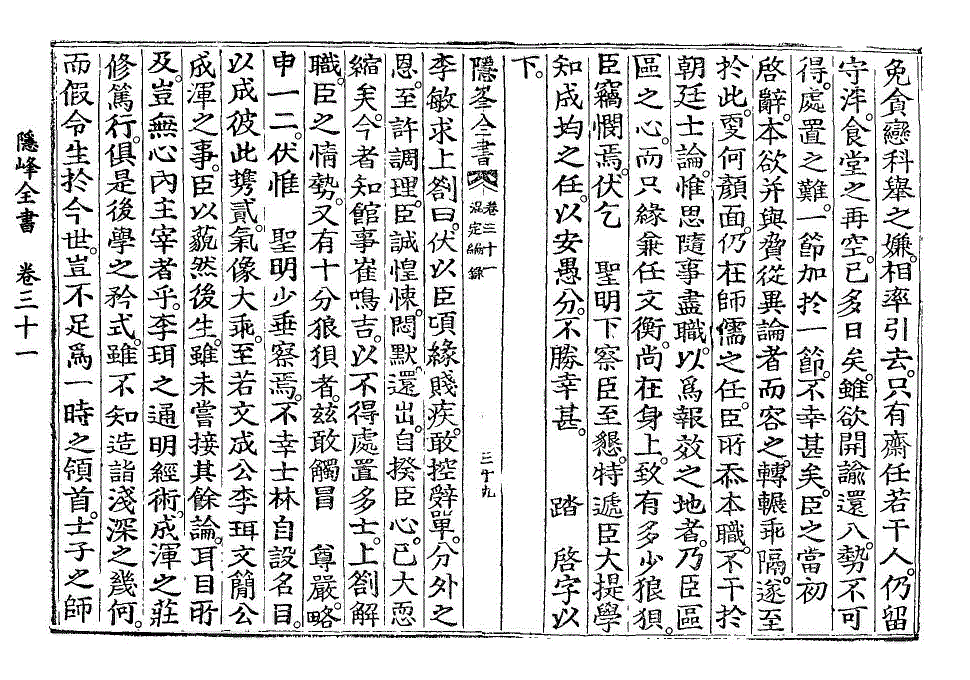 免贪恋科举之嫌。相率引去。只有斋任若干人。仍留守泮。食堂之再空。已多日矣。虽欲开谕还入。势不可得。处置之难。一节加于一节。不幸甚矣。臣之当初 启辞。本欲并与胁从异论者而容之。转辗乖隔。遂至于此。更何颜面。仍在师儒之任。臣所忝本职。不干于朝廷士论。惟思随事尽职。以为报效之地者。乃臣区区之心。而只缘兼任文衡。尚在身上。致有多少狼狈。臣窃悯焉。伏乞 圣明下察臣至恳。特递臣大提学知成均之任。以安愚分。不胜幸甚。 踏 启字以下。
免贪恋科举之嫌。相率引去。只有斋任若干人。仍留守泮。食堂之再空。已多日矣。虽欲开谕还入。势不可得。处置之难。一节加于一节。不幸甚矣。臣之当初 启辞。本欲并与胁从异论者而容之。转辗乖隔。遂至于此。更何颜面。仍在师儒之任。臣所忝本职。不干于朝廷士论。惟思随事尽职。以为报效之地者。乃臣区区之心。而只缘兼任文衡。尚在身上。致有多少狼狈。臣窃悯焉。伏乞 圣明下察臣至恳。特递臣大提学知成均之任。以安愚分。不胜幸甚。 踏 启字以下。李敏求上劄曰。伏以臣顷缘贱疾。敢控辞单。分外之恩。至许调理。臣诚惶悚。闷默。还出。自揆臣心。已大恧缩矣。今者知馆事崔鸣吉。以不得处置多士。上劄解职。臣之情势。又有十分狼狈者。玆敢触冒 尊严。略申一二。伏惟 圣明少垂察焉。不幸士林自设名目。以成彼此携贰。气像大乖。至若文成公李珥文简公成浑之事。臣以藐然后生。虽未尝接其馀论。耳目所及。岂无心内主宰者乎。李珥之通明经术。成浑之庄修笃行。俱是后学之矜式。虽不知造诣浅深之几何。而假令生于今世。岂不足为一时之领首。士子之师
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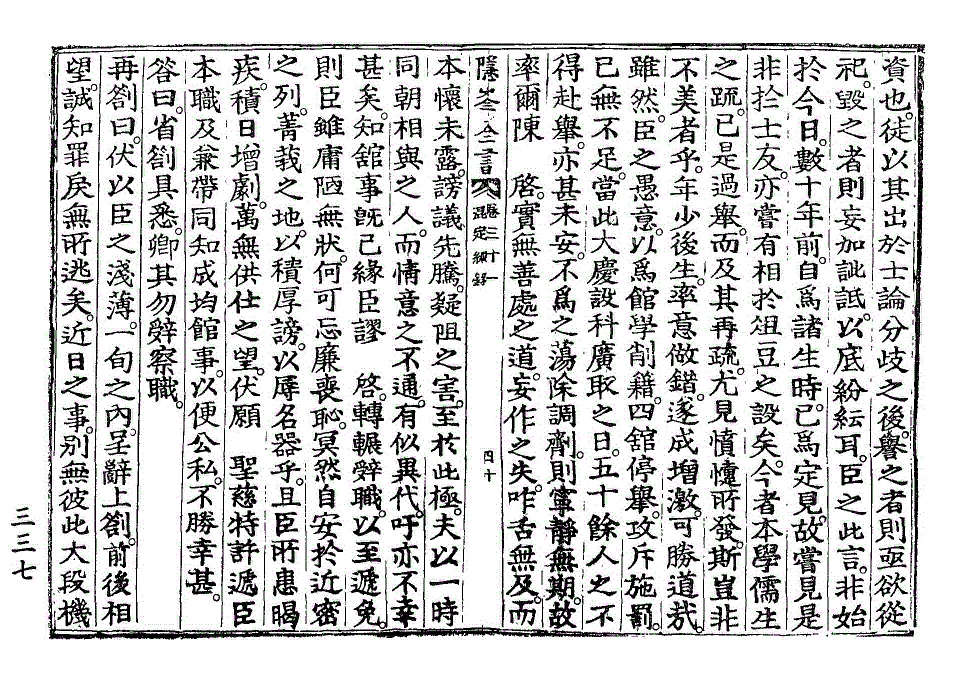 资也。徒以其出于士论分岐之后。誉之者则亟欲从祀。毁之者则妄加訾诋。以底纷纭耳。臣之此言。非始于今日。数十年前。自为诸生时。已为定见。故尝见是非于士友。亦尝有相于俎豆之设矣。今者本学儒生之疏。已是过举。而及其再疏。尤见愤懥所发。斯岂非不美者乎。年少后生。率意做错。遂成增激。可胜道哉。虽然。臣之愚意。以为馆学削籍。四馆停举。攻斥施罚。已无不足。当此大庆设科广取之日。五十馀人之不得赴举。亦甚未安。不为之荡除调剂。则宁静无期。故率尔陈 启。实无善处之道。妄作之失。咋舌无及。而本怀未露。谤议先腾。疑阻之害。至于此极。夫以一时同朝相与之人。而情意之不通。有似异代。吁亦不幸甚矣。知馆事既已缘臣谬 启。转辗辞职。以至递免。则臣虽庸陋无状。何可忘廉丧耻。冥然自安于近密之列。菁莪之地。以积厚谤。以辱名器乎。且臣所患暍疾。积日增剧。万无供仕之望。伏愿 圣慈特许递臣本职及兼带同知成均馆事。以便公私。不胜幸甚。
资也。徒以其出于士论分岐之后。誉之者则亟欲从祀。毁之者则妄加訾诋。以底纷纭耳。臣之此言。非始于今日。数十年前。自为诸生时。已为定见。故尝见是非于士友。亦尝有相于俎豆之设矣。今者本学儒生之疏。已是过举。而及其再疏。尤见愤懥所发。斯岂非不美者乎。年少后生。率意做错。遂成增激。可胜道哉。虽然。臣之愚意。以为馆学削籍。四馆停举。攻斥施罚。已无不足。当此大庆设科广取之日。五十馀人之不得赴举。亦甚未安。不为之荡除调剂。则宁静无期。故率尔陈 启。实无善处之道。妄作之失。咋舌无及。而本怀未露。谤议先腾。疑阻之害。至于此极。夫以一时同朝相与之人。而情意之不通。有似异代。吁亦不幸甚矣。知馆事既已缘臣谬 启。转辗辞职。以至递免。则臣虽庸陋无状。何可忘廉丧耻。冥然自安于近密之列。菁莪之地。以积厚谤。以辱名器乎。且臣所患暍疾。积日增剧。万无供仕之望。伏愿 圣慈特许递臣本职及兼带同知成均馆事。以便公私。不胜幸甚。答曰。省劄具悉。卿其勿辞察职。
再劄曰。伏以臣之浅薄。一旬之内。呈辞上劄。前后相望。诚知罪戾无所逃矣。近日之事。别无彼此大段机
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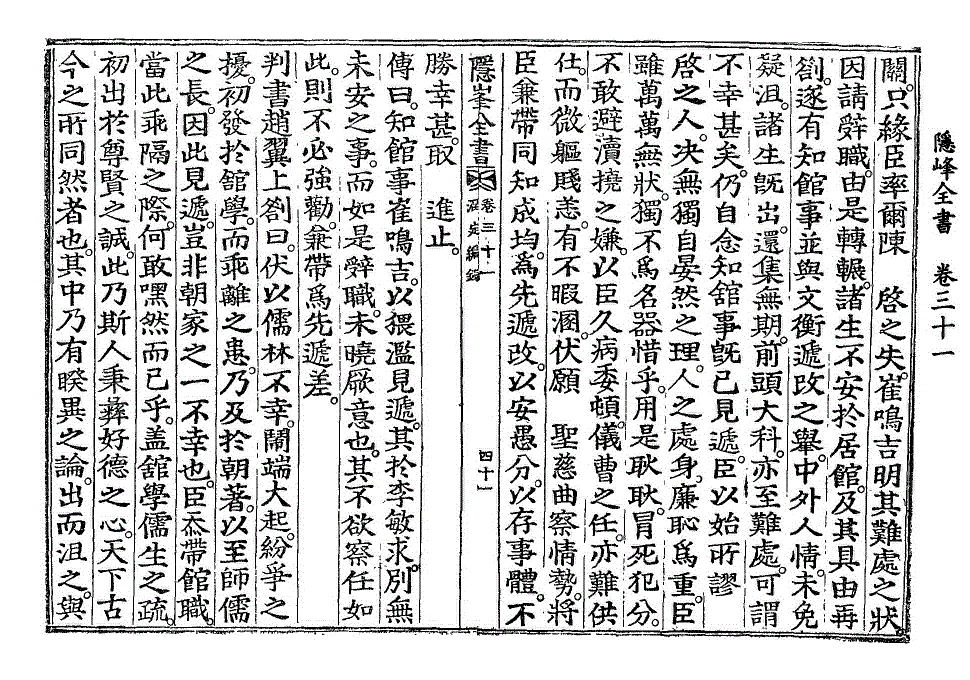 关。只缘臣率尔陈 启之失。崔鸣吉明其难处之状。因请辞职。由是转辗。诸生不安于居馆。及其具由再劄。遂有知馆事并与文衡递改之举。中外人情。未免疑沮。诸生既出。还集无期。前头大科。亦至难处。可谓不幸甚矣。仍自念知馆事既已见递。臣以始所谬 启之人。决无独自晏然之理。人之处身。廉耻为重。臣虽万万无状。独不为名器惜乎。用是耿耿。冒死犯分。不敢避渎挠之嫌。以臣久病委顿。仪曹之任。亦难供仕。而微躯贱恙。有不暇溷。伏愿 圣慈曲察情势。将臣兼带同知成均。为先递改。以安愚分。以存事体。不胜幸甚。取 进止。
关。只缘臣率尔陈 启之失。崔鸣吉明其难处之状。因请辞职。由是转辗。诸生不安于居馆。及其具由再劄。遂有知馆事并与文衡递改之举。中外人情。未免疑沮。诸生既出。还集无期。前头大科。亦至难处。可谓不幸甚矣。仍自念知馆事既已见递。臣以始所谬 启之人。决无独自晏然之理。人之处身。廉耻为重。臣虽万万无状。独不为名器惜乎。用是耿耿。冒死犯分。不敢避渎挠之嫌。以臣久病委顿。仪曹之任。亦难供仕。而微躯贱恙。有不暇溷。伏愿 圣慈曲察情势。将臣兼带同知成均。为先递改。以安愚分。以存事体。不胜幸甚。取 进止。传曰。知馆事崔鸣吉。以猥滥见递。其于李敏求。别无未安之事。而如是辞职。未晓厥意也。其不欲察任如此。则不必强劝。兼带为先递差。
判书赵翼上劄曰。伏以儒林不幸。闹端大起。纷争之扰。初发于馆学。而乖离之患。乃及于朝著。以至师儒之长。因此见递。岂非朝家之一不幸也。臣忝带馆职。当此乖隔之际。何敢默然而已乎。盖馆学儒生之疏。初出于尊贤之诚。此乃斯人秉彝好德之心。天下古今之所同然者也。其中乃有睽异之论。出而沮之。与
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38L 页
 之相持。其势不容并立。必抑彼而后此说乃行。然则其辞而斥之。乌得已乎。然只是斥其言。使不得害正也。岂是逐其人。使不得留馆乎。其异论之人。自皆出去。谓为驱逐耳。夫二臣道德浅深高下。固非人人之所得知也。然其为学古修善之人。则实举国之所共知也。彼异论者如曰吾不知其必合于从祀。则自其所见不逮也。亦何可非也。至于陷害之。则决是不美也。四馆并起。互为停举。其停也虽彼此皆为。其中自有是非。一则尊贤。一则陷贤。一则停陷贤者。一则停尊贤者。而彼此儒生。皆止其圆点。以致食堂空虚。为师儒之任者。岂可无处置之道哉。顷日本馆之 启。出于知馆之手。而分别可否。或停或解。其是者固当解释。而其非者亦分轻重。许其自新。使同赴试围。既有以卞别之。又有以宽容之。其处置可谓得宜矣。其后都承旨李敏求因异论儒生再疏。请令知馆更议处之。其疏辞悖慢。极其辱骂。少无悛心。如此人虽使登科。何所用之。承旨之意。虽欲使人皆赴举。治世之道。岂可都不分善恶是非而使之并进哉。崔鸣吉之不敢承当。实所当然。第其辞气之间。失于和平。不能只陈当否。乃复并辞其职。以致上激 天怒。至下驱
之相持。其势不容并立。必抑彼而后此说乃行。然则其辞而斥之。乌得已乎。然只是斥其言。使不得害正也。岂是逐其人。使不得留馆乎。其异论之人。自皆出去。谓为驱逐耳。夫二臣道德浅深高下。固非人人之所得知也。然其为学古修善之人。则实举国之所共知也。彼异论者如曰吾不知其必合于从祀。则自其所见不逮也。亦何可非也。至于陷害之。则决是不美也。四馆并起。互为停举。其停也虽彼此皆为。其中自有是非。一则尊贤。一则陷贤。一则停陷贤者。一则停尊贤者。而彼此儒生。皆止其圆点。以致食堂空虚。为师儒之任者。岂可无处置之道哉。顷日本馆之 启。出于知馆之手。而分别可否。或停或解。其是者固当解释。而其非者亦分轻重。许其自新。使同赴试围。既有以卞别之。又有以宽容之。其处置可谓得宜矣。其后都承旨李敏求因异论儒生再疏。请令知馆更议处之。其疏辞悖慢。极其辱骂。少无悛心。如此人虽使登科。何所用之。承旨之意。虽欲使人皆赴举。治世之道。岂可都不分善恶是非而使之并进哉。崔鸣吉之不敢承当。实所当然。第其辞气之间。失于和平。不能只陈当否。乃复并辞其职。以致上激 天怒。至下驱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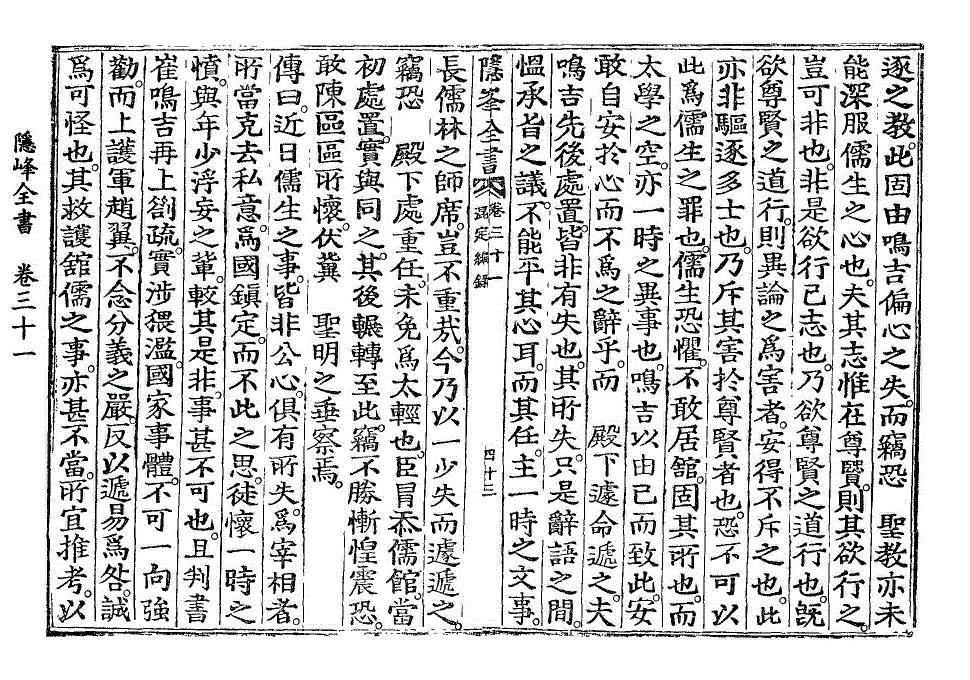 逐之教。此固由鸣吉偏心之失。而窃恐 圣教亦未能深服儒生之心也。夫其志惟在尊贤。则其欲行之。岂可非也。非是欲行己志也。乃欲尊贤之道行也。既欲尊贤之道行。则异论之为害者。安得不斥之也。此亦非驱逐多士也。乃斥其害于尊贤者也。恐不可以此为儒生之罪也。儒生恐惧。不敢居馆。固其所也。而太学之空。亦一时之异事也。鸣吉以由己而致此。安敢自安于心而不为之辞乎。而 殿下遽命递之。夫鸣吉先后处置。皆非有失也。其所失。只是辞语之间。愠承旨之议。不能平其心耳。而其任。主一时之文事。长儒林之师席。岂不重哉。今乃以一少失而遽递之。窃恐 殿下处重任。未免为太轻也。臣冒忝儒馆。当初处置。实与同之。其后辗转至此。窃不胜惭惶震恐。敢陈区区所怀。伏冀 圣明之垂察焉。
逐之教。此固由鸣吉偏心之失。而窃恐 圣教亦未能深服儒生之心也。夫其志惟在尊贤。则其欲行之。岂可非也。非是欲行己志也。乃欲尊贤之道行也。既欲尊贤之道行。则异论之为害者。安得不斥之也。此亦非驱逐多士也。乃斥其害于尊贤者也。恐不可以此为儒生之罪也。儒生恐惧。不敢居馆。固其所也。而太学之空。亦一时之异事也。鸣吉以由己而致此。安敢自安于心而不为之辞乎。而 殿下遽命递之。夫鸣吉先后处置。皆非有失也。其所失。只是辞语之间。愠承旨之议。不能平其心耳。而其任。主一时之文事。长儒林之师席。岂不重哉。今乃以一少失而遽递之。窃恐 殿下处重任。未免为太轻也。臣冒忝儒馆。当初处置。实与同之。其后辗转至此。窃不胜惭惶震恐。敢陈区区所怀。伏冀 圣明之垂察焉。传曰。近日儒生之事。皆非公心。俱有所失。为宰相者。所当克去私意。为国镇定。而不此之思。徒怀一时之愤。与年少浮妄之辈。较其是非。事甚不可也。且判书崔鸣吉再上劄疏。实涉猥滥。国家事体。不可一向强劝。而上护军赵翼。不念分义之严。反以递易为咎。诚为可怪也。其救护馆儒之事。亦甚不当。所宜推考。以
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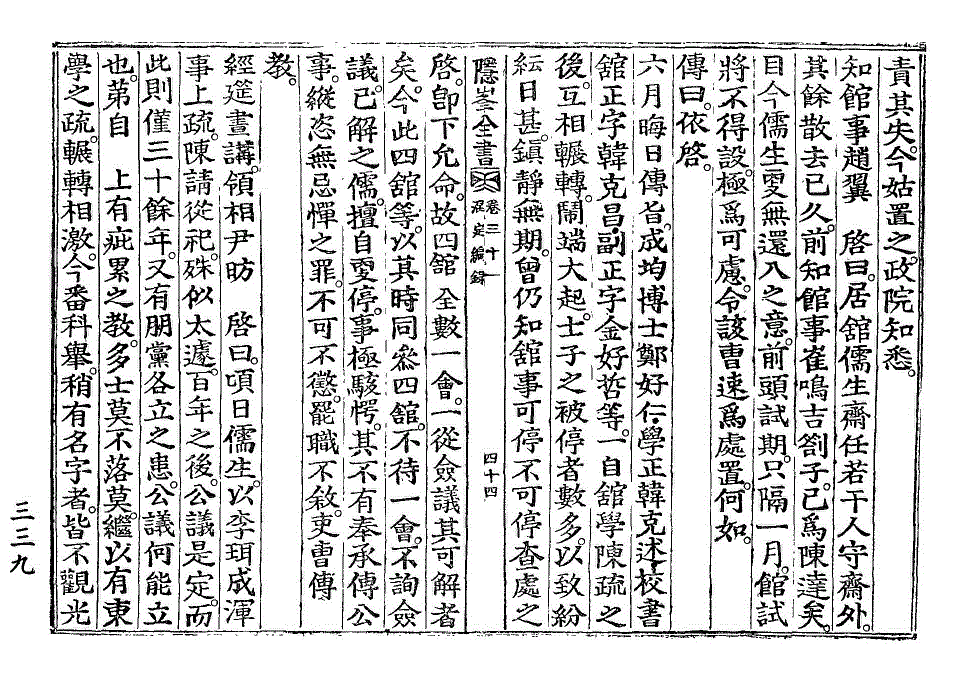 责其失。今姑置之。政院知悉。
责其失。今姑置之。政院知悉。知馆事赵翼 启曰。居馆儒生斋任若干人守斋外。其馀散去已久。前知馆事崔鸣吉劄子。已为陈达矣。目今儒生更无还入之意。前头试期。只隔一月。馆试将不得设。极为可虑。令该曹速为处置。何如。
传曰。依启。
六月晦日传旨。成均博士郑好仁,学正韩克述,校书馆正字韩克昌,副正字金好哲等。一自馆学陈疏之后。互相辗转。闹端大起。士子之被停者数多。以致纷纭日甚。镇静无期。曾仍知馆事可停不可停查处之启。即下允命。故四馆全数一会。一从佥议其可解者矣。今此四馆等。以其时同参四馆。不待一会。不询佥议。已解之儒。擅自更停。事极骇愕。其不有奉承传公事。纵恣无忌惮之罪。不可不惩。罢职不叙。吏曹传 教。
经筵昼讲。领相尹昉 启曰。顷日儒生。以李珥成浑事上疏。陈请从祀。殊似太遽。百年之后。公议是定。而此则仅三十馀年。又有朋党各立之患。公议何能立也。第自 上有疵累之教。多士莫不落莫。继以有东学之疏。辗转相激。今番科举。稍有名字者。皆不观光
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40H 页
 矣。当初多士既以驱逐之 教为未安。又 下去其馆试之命。故多士之意。 圣明不欲使渠辈观光。故皆不赴举。 上意则岂必如渠所料乎。东学疏儒。以公议非之故。亦不赴举。自 上必未知之矣。臣意则多士虽有过激之举。不可不优容也。
矣。当初多士既以驱逐之 教为未安。又 下去其馆试之命。故多士之意。 圣明不欲使渠辈观光。故皆不赴举。 上意则岂必如渠所料乎。东学疏儒。以公议非之故。亦不赴举。自 上必未知之矣。臣意则多士虽有过激之举。不可不优容也。四学儒生一百四十馀人上疏。其略曰。伏以臣等。顷因多士会集之日。以先正臣文成公李珥文简公成浑从祀 文庙之事。齐声合辞。伏阙陈章。而 天听邈然。少无收省之意。臣等相与咨嗟而言曰。岂多士之诚有所未尽耶。以 殿下之圣。非不知两臣之贤优入于从祀之列。而不即 允许者。必以臣等为不足以知两臣之贤也。将何颜面复入首善之地乎。欲从 阙下分散。而仍窃思惟。我 殿下尊道崇儒之德。实迈隆古。今之不即 允许。特出于难慎之意。姑还黉序。以俟 睿断。臣等之所以望于 殿下者。其亦尽矣。不料玆者。因知馆事崔鸣吉劄子。乃有欲行己志。驱逐多士之 教。噫。欲行己志。驱逐多士。则其设心行事。果何如也。 殿下其不以士子待泮宫之士矣。平昔培养之意。恐不当如是也。在泮之士。身负如许罪目。而 天威之下。不敢自列。惊惶奔溃。席藁
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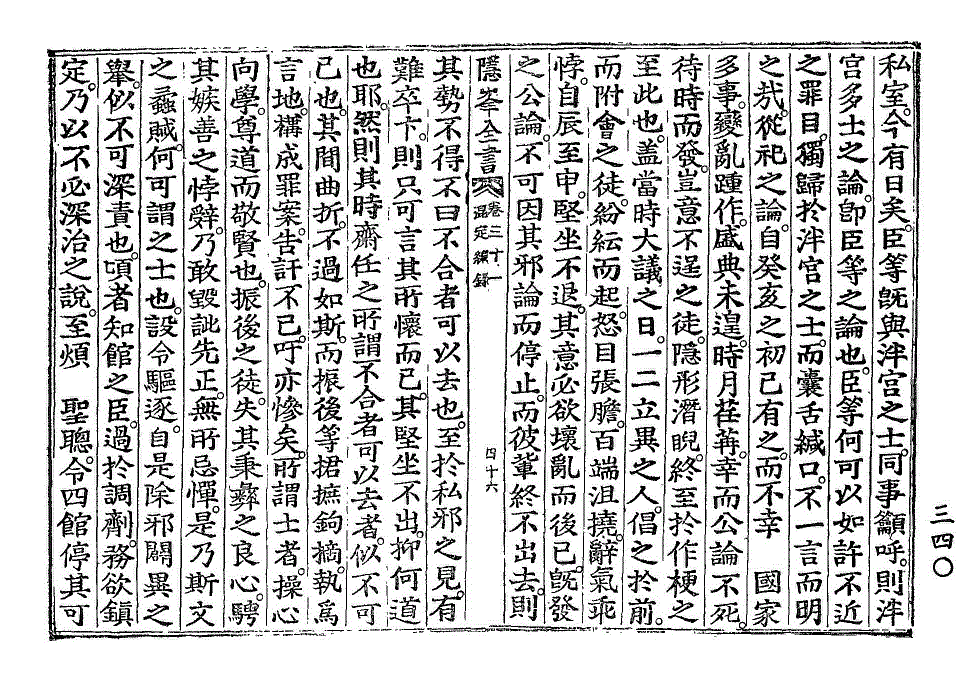 私室。今有日矣。臣等既与泮宫之士。同事吁呼。则泮宫多士之论。即臣等之论也。臣等何可以如许不近之罪目。独归于泮宫之士。而囊舌缄口。不一言而明之哉。从祀之论。自癸亥之初已有之。而不幸 国家多事。变乱踵作。盛典未遑。时月荏苒。幸而公论不死。待时而发。岂意不逞之徒。隐形潜睨。终至于作梗之至此也。盖当时大议之日。一二立异之人。倡之于前。而附会之徒。纷纭而起。怒目张胆。百端沮挠。辞气乖悖。自辰至申。坚坐不退。其意必欲坏乱而后已。既发之公论。不可因其邪论而停止。而彼辈终不出去。则其势不得不曰不合者可以去也。至于私邪之见。有难卒卞。则只可言其所怀而已。其坚坐不出。抑何道也耶。然则其时斋任之所谓不合者可以去者。似不可已也。其间曲折。不过如斯。而振后等捃摭钩摘。执为言地。构成罪案。告讦不已。吁亦惨矣。所谓士者。操心向学。尊道而敬贤也。振后之徒。失其秉彝之良心。骋其嫉善之悖辞。乃敢毁訾先正。无所忌惮。是乃斯文之蟊贼。何可谓之士也。设令驱逐。自是除邪辟异之举。似不可深责也。顷者知馆之臣。过于调剂。务欲镇定。乃以不必深治之说。至烦 圣聪。令四馆停其可
私室。今有日矣。臣等既与泮宫之士。同事吁呼。则泮宫多士之论。即臣等之论也。臣等何可以如许不近之罪目。独归于泮宫之士。而囊舌缄口。不一言而明之哉。从祀之论。自癸亥之初已有之。而不幸 国家多事。变乱踵作。盛典未遑。时月荏苒。幸而公论不死。待时而发。岂意不逞之徒。隐形潜睨。终至于作梗之至此也。盖当时大议之日。一二立异之人。倡之于前。而附会之徒。纷纭而起。怒目张胆。百端沮挠。辞气乖悖。自辰至申。坚坐不退。其意必欲坏乱而后已。既发之公论。不可因其邪论而停止。而彼辈终不出去。则其势不得不曰不合者可以去也。至于私邪之见。有难卒卞。则只可言其所怀而已。其坚坐不出。抑何道也耶。然则其时斋任之所谓不合者可以去者。似不可已也。其间曲折。不过如斯。而振后等捃摭钩摘。执为言地。构成罪案。告讦不已。吁亦惨矣。所谓士者。操心向学。尊道而敬贤也。振后之徒。失其秉彝之良心。骋其嫉善之悖辞。乃敢毁訾先正。无所忌惮。是乃斯文之蟊贼。何可谓之士也。设令驱逐。自是除邪辟异之举。似不可深责也。顷者知馆之臣。过于调剂。务欲镇定。乃以不必深治之说。至烦 圣聪。令四馆停其可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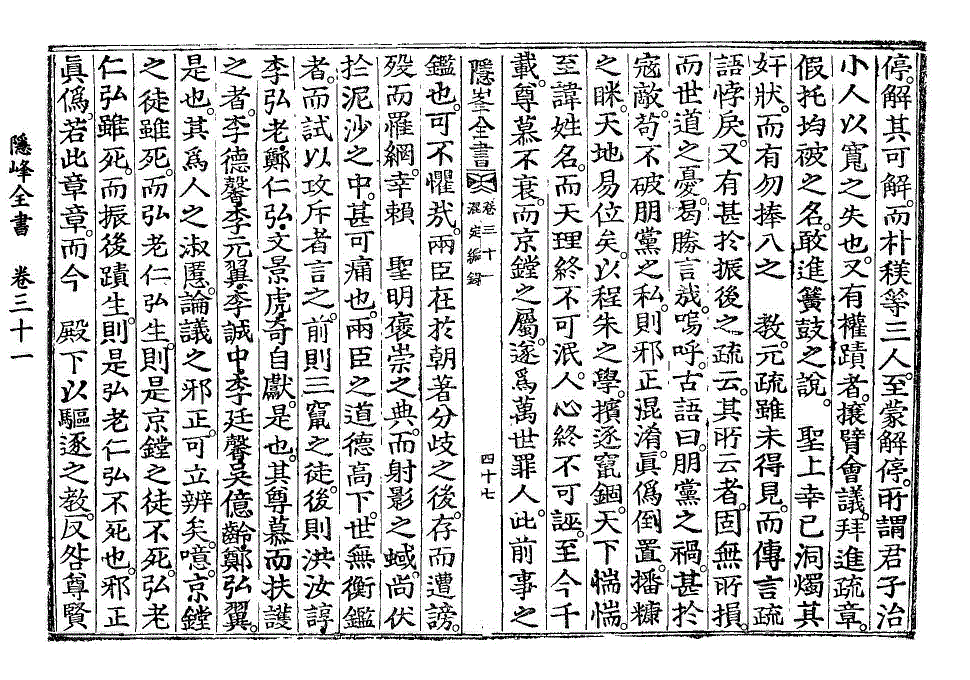 停。解其可解。而朴𥠦等三人。至蒙解停。所谓君子治小人以宽之失也。又有权迹者。攘臂会议。拜进疏章。假托均被之名。敢进簧鼓之说。 圣上幸已洞烛其奸状。而有勿捧入之 教。元疏虽未得见。而传言疏语悖戾。又有甚于振后之疏云。其所云者。固无所损。而世道之忧。曷胜言哉。呜呼。古语曰。朋党之祸。甚于寇敌。苟不破朋党之私。则邪正混淆。真伪倒置。播糠之眯。天地易位矣。以程朱之学。摈逐窜锢。天下惴惴。至讳姓名。而天理终不可泯。人心终不可诬。至今千载。尊慕不衰。而京镗之属。遂为万世罪人。此前事之鉴也。可不惧哉。两臣在于朝著分岐之后。存而遭谤。殁而罹网。幸赖 圣明褒崇之典。而射影之蜮。尚伏于泥沙之中。甚可痛也。两臣之道德高下。世无衡鉴者。而试以攻斥者言之。前则三窜之徒。后则洪汝谆,李弘老,郑仁弘,文景虎,奇自献。是也。其尊慕而扶护之者。李德馨,李元翼,李诚中,李廷馨,吴亿龄,郑弘翼。是也。其为人之淑慝。论议之邪正。可立辨矣。噫。京镗之徒虽死。而弘老仁弘生。则是京镗之徒不死。弘老仁弘虽死。而振后迹生。则是弘老仁弘不死也。邪正真伪。若此章章。而今 殿下以驱逐之教。反咎尊贤
停。解其可解。而朴𥠦等三人。至蒙解停。所谓君子治小人以宽之失也。又有权迹者。攘臂会议。拜进疏章。假托均被之名。敢进簧鼓之说。 圣上幸已洞烛其奸状。而有勿捧入之 教。元疏虽未得见。而传言疏语悖戾。又有甚于振后之疏云。其所云者。固无所损。而世道之忧。曷胜言哉。呜呼。古语曰。朋党之祸。甚于寇敌。苟不破朋党之私。则邪正混淆。真伪倒置。播糠之眯。天地易位矣。以程朱之学。摈逐窜锢。天下惴惴。至讳姓名。而天理终不可泯。人心终不可诬。至今千载。尊慕不衰。而京镗之属。遂为万世罪人。此前事之鉴也。可不惧哉。两臣在于朝著分岐之后。存而遭谤。殁而罹网。幸赖 圣明褒崇之典。而射影之蜮。尚伏于泥沙之中。甚可痛也。两臣之道德高下。世无衡鉴者。而试以攻斥者言之。前则三窜之徒。后则洪汝谆,李弘老,郑仁弘,文景虎,奇自献。是也。其尊慕而扶护之者。李德馨,李元翼,李诚中,李廷馨,吴亿龄,郑弘翼。是也。其为人之淑慝。论议之邪正。可立辨矣。噫。京镗之徒虽死。而弘老仁弘生。则是京镗之徒不死。弘老仁弘虽死。而振后迹生。则是弘老仁弘不死也。邪正真伪。若此章章。而今 殿下以驱逐之教。反咎尊贤隐峰全书卷三十一 第 3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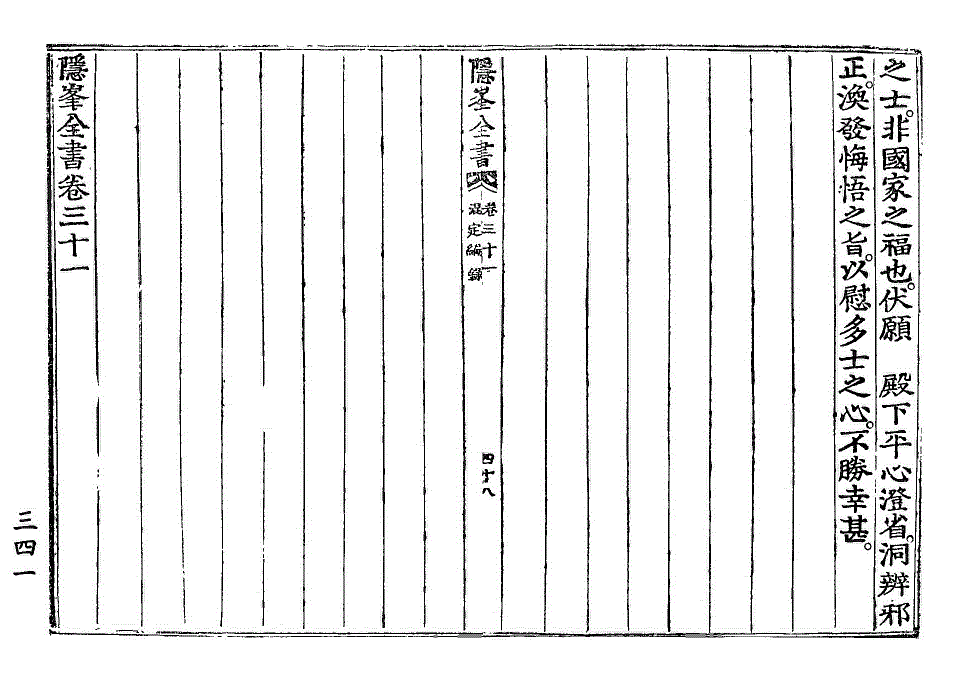 之士。非国家之福也。伏愿 殿下平心澄省。洞辨邪正。涣发悔悟之旨。以慰多士之心。不胜幸甚。
之士。非国家之福也。伏愿 殿下平心澄省。洞辨邪正。涣发悔悟之旨。以慰多士之心。不胜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