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x 页
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混定编录(后集)
混定编录(后集)
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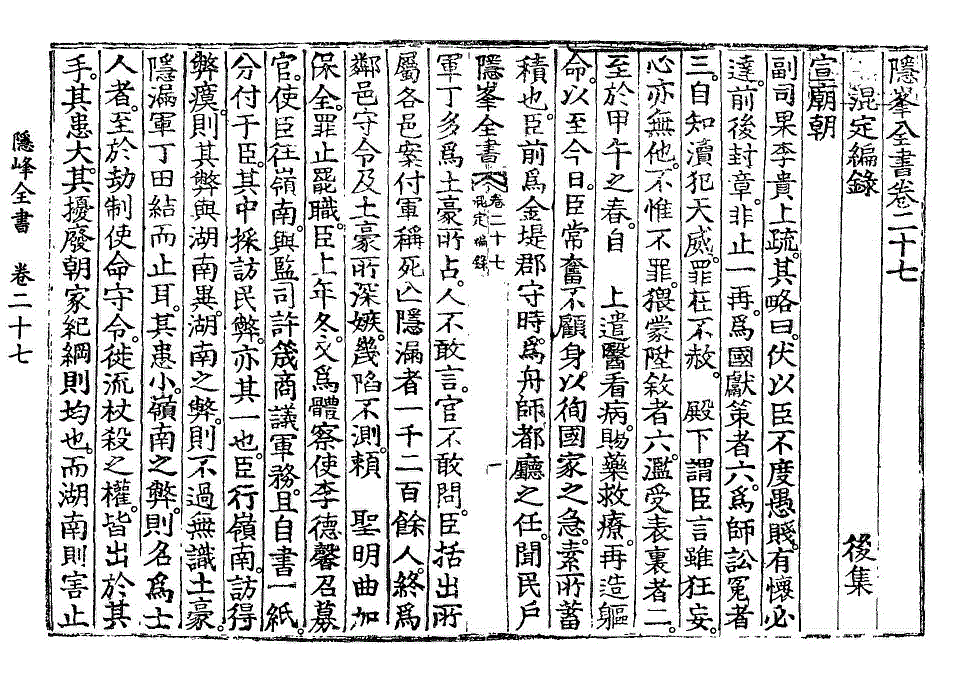 宣庙朝
宣庙朝副司果李贵上疏。其略曰。伏以臣不度愚贱。有怀必达。前后封章。非止一再。为国献策者六。为师讼冤者三。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 殿下谓臣言虽狂妄。心亦无他。不惟不罪。猥蒙升叙者六。滥受表里者二。至于甲午之春。自 上遣医看病。赐药救疗。再造躯命。以至今日。臣常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素所蓄积也。臣前为金堤郡守时。为舟师都厅之任。闻民户军丁多为土豪所占。人不敢言。官不敢问。臣括出所属各邑案付军称死亡隐漏者一千二百馀人。终为邻邑守令及土豪所深嫉。几陷不测。赖 圣明曲加保全。罪止罢职。臣上年冬。又为体察使李德馨召募官。使臣往岭南。与监司许筬商议军务。且自书一纸。分付于臣。其中采访民弊。亦其一也。臣行岭南。访得弊瘼。则其弊与湖南异。湖南之弊。则不过无识土豪。隐漏军丁田结而止耳。其患小。岭南之弊。则名为士人者。至于劫制使命守令。徙流杖杀之权。皆出于其手。其患大。其扰废朝家纪纲则均也。而湖南则害止
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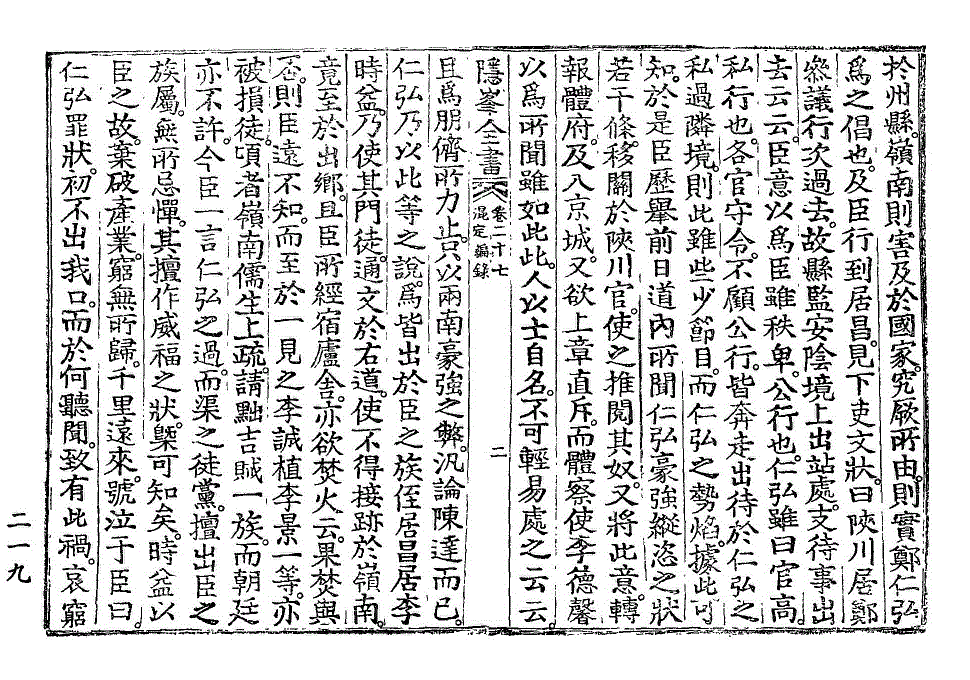 于州县。岭南则害及于国家。究厥所由。则实郑仁弘为之倡也。及臣行到居昌。见下吏文状。曰陜川居郑参议行次过去。故县监安阴境上出站处。支待事出去云云。臣意以为臣虽秩卑。公行也。仁弘虽曰官高。私行也。各官守令。不顾公行。皆奔走出待于仁弘之私过邻境。则此虽些少节目。而仁弘之势焰。据此可知。于是臣历举前日道内所闻仁弘豪强纵恣之状若干条。移关于陜川官。使之推阅其奴。又将此意。转报体府。及入京城。又欲上章直斥。而体察使李德馨以为所闻虽如此此。人以士自名。不可轻易处之云云。且为朋侪所力止。只以两南豪强之弊。汎论陈达而已。仁弘乃以此等之说。为皆出于臣之族侄居昌居李时益。乃使其门徒。通文于右道。使不得接迹于岭南。竟至于出乡。且臣所经宿庐舍。亦欲焚火云。果焚与否。则臣远不知。而至于一见之李诚植李景一等。亦被损徒。顷者岭南儒生上疏。请黜吉贼一族。而朝廷亦不许。今臣一言仁弘之过。而渠之徒党。擅出臣之族属。无所忌惮。其擅作威福之状。槩可知矣。时益以臣之故。弃破产业。穷无所归。千里远来。号泣于臣曰。仁弘罪状。初不出我口。而于何听闻。致有此祸。哀穷
于州县。岭南则害及于国家。究厥所由。则实郑仁弘为之倡也。及臣行到居昌。见下吏文状。曰陜川居郑参议行次过去。故县监安阴境上出站处。支待事出去云云。臣意以为臣虽秩卑。公行也。仁弘虽曰官高。私行也。各官守令。不顾公行。皆奔走出待于仁弘之私过邻境。则此虽些少节目。而仁弘之势焰。据此可知。于是臣历举前日道内所闻仁弘豪强纵恣之状若干条。移关于陜川官。使之推阅其奴。又将此意。转报体府。及入京城。又欲上章直斥。而体察使李德馨以为所闻虽如此此。人以士自名。不可轻易处之云云。且为朋侪所力止。只以两南豪强之弊。汎论陈达而已。仁弘乃以此等之说。为皆出于臣之族侄居昌居李时益。乃使其门徒。通文于右道。使不得接迹于岭南。竟至于出乡。且臣所经宿庐舍。亦欲焚火云。果焚与否。则臣远不知。而至于一见之李诚植李景一等。亦被损徒。顷者岭南儒生上疏。请黜吉贼一族。而朝廷亦不许。今臣一言仁弘之过。而渠之徒党。擅出臣之族属。无所忌惮。其擅作威福之状。槩可知矣。时益以臣之故。弃破产业。穷无所归。千里远来。号泣于臣曰。仁弘罪状。初不出我口。而于何听闻。致有此祸。哀穷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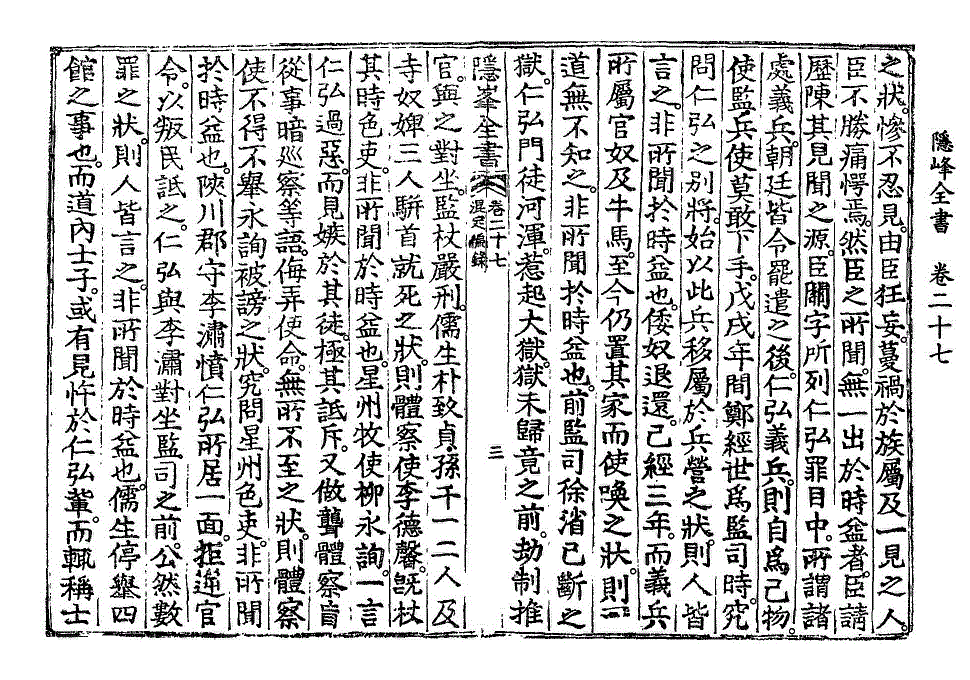 之状。惨不忍见。由臣狂妄。蔓祸于族属及一见之人。臣不胜痛愕焉。然臣之所闻。无一出于时益者。臣请历陈其见闻之源。臣关字所列仁弘罪目中。所谓诸处义兵。朝廷皆令罢遣之后。仁弘义兵。则自为己物。使监,兵使莫敢下手。戊戌年间郑经世为监司时。究问仁弘之别将。始以此兵移属于兵营之状。则人皆言之。非所闻于时益也。倭奴退还。已经三年。而义兵所属官奴及牛马。至今仍置其家而使唤之状。则▒道无不知之。非所闻于时益也。前监司徐渻已断之狱。仁弘门徒河浑。惹起大狱。狱未归竟之前。劫制推官。与之对坐。监杖严刑。儒生朴致贞,孙千一二人及寺奴婢三人骈首就死之状。则体察使李德声。既杖其时色吏。非所闻于时益也。星州牧使柳永询。一言仁弘过恶。而见嫉于其徒。极其诋斥。又做聋体察盲从事暗巡察等语。侮弄使命。无所不至之状。则体察使不得不举永询被谤之状。究问星州色吏。非所闻于时益也。陜川郡守李潚愤仁弘所居一面。拒逆官令。以叛民诋之。仁弘与李潚对坐监司之前。公然数罪之状。则人皆言之。非所闻于时益也。儒生停举四馆之事也。而道内士子。或有见忤于仁弘辈。而辄称士
之状。惨不忍见。由臣狂妄。蔓祸于族属及一见之人。臣不胜痛愕焉。然臣之所闻。无一出于时益者。臣请历陈其见闻之源。臣关字所列仁弘罪目中。所谓诸处义兵。朝廷皆令罢遣之后。仁弘义兵。则自为己物。使监,兵使莫敢下手。戊戌年间郑经世为监司时。究问仁弘之别将。始以此兵移属于兵营之状。则人皆言之。非所闻于时益也。倭奴退还。已经三年。而义兵所属官奴及牛马。至今仍置其家而使唤之状。则▒道无不知之。非所闻于时益也。前监司徐渻已断之狱。仁弘门徒河浑。惹起大狱。狱未归竟之前。劫制推官。与之对坐。监杖严刑。儒生朴致贞,孙千一二人及寺奴婢三人骈首就死之状。则体察使李德声。既杖其时色吏。非所闻于时益也。星州牧使柳永询。一言仁弘过恶。而见嫉于其徒。极其诋斥。又做聋体察盲从事暗巡察等语。侮弄使命。无所不至之状。则体察使不得不举永询被谤之状。究问星州色吏。非所闻于时益也。陜川郡守李潚愤仁弘所居一面。拒逆官令。以叛民诋之。仁弘与李潚对坐监司之前。公然数罪之状。则人皆言之。非所闻于时益也。儒生停举四馆之事也。而道内士子。或有见忤于仁弘辈。而辄称士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20L 页
 林停举之状。则一道之所共言。非所闻于时益也。今陜川郡守李馪赴任之初。仁弘徒党等捉致本邑下吏。数罪决杖之状。则人人之所共言。非所闻于时益也。至于近邑士子之不从己意者。辄称士子损徒。而顷者。文伟,李景一等十馀人。不参文景虎之疏。而并被损徒之事。则通文行于一道。非所闻于时益也。时益当初非不知此等罪恶。而畏仁弘之威势。不敢以语臣。至是。始言仁弘以被虏妇女。胁嫁逃唐兵之看地理者。又以士族之女。劫婚微贱人之救己病者。且以其徒党为风宪有司。使之出入官府。胁制使命守令云云。如使时益初言此等罪状于臣。则其时关字中。岂置而不论乎。臣之前日所斥仁弘之罪。皆得于一道传播之说。非独臣闻之。前后往来大小使命。无不言之。而仁弘辈独归罪于时益。不亦冤乎。若渠有大段恶行。犯于纲常者。则容或有黜损之举。而至以言己之恶者。任其黜损而钳制人口者。则臣未之知也。假使时益实言于臣。而臣既受体府分付。则臣之历举所闻。移文本官。使之推问其奴。转报本府者。亦是公事场当然者也。乃以移关之故。其祸延于族侄。而不得接迹于道内。至于一见臣面之李诚植等。亦不容
林停举之状。则一道之所共言。非所闻于时益也。今陜川郡守李馪赴任之初。仁弘徒党等捉致本邑下吏。数罪决杖之状。则人人之所共言。非所闻于时益也。至于近邑士子之不从己意者。辄称士子损徒。而顷者。文伟,李景一等十馀人。不参文景虎之疏。而并被损徒之事。则通文行于一道。非所闻于时益也。时益当初非不知此等罪恶。而畏仁弘之威势。不敢以语臣。至是。始言仁弘以被虏妇女。胁嫁逃唐兵之看地理者。又以士族之女。劫婚微贱人之救己病者。且以其徒党为风宪有司。使之出入官府。胁制使命守令云云。如使时益初言此等罪状于臣。则其时关字中。岂置而不论乎。臣之前日所斥仁弘之罪。皆得于一道传播之说。非独臣闻之。前后往来大小使命。无不言之。而仁弘辈独归罪于时益。不亦冤乎。若渠有大段恶行。犯于纲常者。则容或有黜损之举。而至以言己之恶者。任其黜损而钳制人口者。则臣未之知也。假使时益实言于臣。而臣既受体府分付。则臣之历举所闻。移文本官。使之推问其奴。转报本府者。亦是公事场当然者也。乃以移关之故。其祸延于族侄。而不得接迹于道内。至于一见臣面之李诚植等。亦不容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21H 页
 于一乡。岂意嬴秦收司之律。乃为匹夫窃弄之资乎。时益是京居士族之流寓者。而一触其怒。祸至于此。况遐远之地。本土之人。则徒流杖杀之权。专出于此辈。虽有冤抑之事。谁因而谁极乎。至于河浑胁迫推官。既杀儒生朴致贞等二人及公贱三人。而其中军功奉事史奉礼者。独脱虎口。来呈法司。法司囚河浑之子大受。欲治其罪。河浑愤奉礼之呈法司。又胁推官。杖杀奉礼之老母。设使奉礼实有其罪。以子之罪而杀其老母。逆贼缘坐之外。国法之所未有也。而此辈忍为之。不亦惨乎。设使被杀公贱三人。实有叛主之罪。至于朴致贞。则只以其婢作妾之故。又从而杀之。呜呼。无罪而杀士。国君尚不敢为。况匹夫乎。国家三尺。是何等物。而为此辈报复私怨之资。肆然而莫之禁乎。臣不胜痛心焉。致贞,千一之子弟亲属。非不欲为父兄报雠。而又恐雠未报而身先死。又如史奉礼之母祸。故终莫敢出头讼冤。如此等事。则虽仁弘之亲党如朴惺辈。亦莫不称冤。而仁弘则与河浑邻居。朝夕相从。反助其恶。至于台论既发体府回启之后。自知理屈。乞和退讼。而官不得问。无辜五人之命。不亦哀哉。昔汉朝郭解门客。为解杀人。武帝断之曰。解之
于一乡。岂意嬴秦收司之律。乃为匹夫窃弄之资乎。时益是京居士族之流寓者。而一触其怒。祸至于此。况遐远之地。本土之人。则徒流杖杀之权。专出于此辈。虽有冤抑之事。谁因而谁极乎。至于河浑胁迫推官。既杀儒生朴致贞等二人及公贱三人。而其中军功奉事史奉礼者。独脱虎口。来呈法司。法司囚河浑之子大受。欲治其罪。河浑愤奉礼之呈法司。又胁推官。杖杀奉礼之老母。设使奉礼实有其罪。以子之罪而杀其老母。逆贼缘坐之外。国法之所未有也。而此辈忍为之。不亦惨乎。设使被杀公贱三人。实有叛主之罪。至于朴致贞。则只以其婢作妾之故。又从而杀之。呜呼。无罪而杀士。国君尚不敢为。况匹夫乎。国家三尺。是何等物。而为此辈报复私怨之资。肆然而莫之禁乎。臣不胜痛心焉。致贞,千一之子弟亲属。非不欲为父兄报雠。而又恐雠未报而身先死。又如史奉礼之母祸。故终莫敢出头讼冤。如此等事。则虽仁弘之亲党如朴惺辈。亦莫不称冤。而仁弘则与河浑邻居。朝夕相从。反助其恶。至于台论既发体府回启之后。自知理屈。乞和退讼。而官不得问。无辜五人之命。不亦哀哉。昔汉朝郭解门客。为解杀人。武帝断之曰。解之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21L 页
 门客杀人。解虽不杀。其实解杀之。遂罪郭解。今日仁弘之徒党。或为仁弘而任意黜人。或藉其势而擅杀士人。则仁弘乌得无罪乎。噫。使皋陶为士。则杀人之罪。虽天子之父。犹不得免。而况河浑辈。藉仁弘之势。杀人无忌。而人莫敢言。其可谓有国法乎。此辈之气势。崇长不已。则臣恐威福下移。而朝廷命令。不得行于岭南也。设令臣之所言。虚妄不实。而为仁弘者。果是善人。则当自反于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也。而乃移怒于族人。则至于黜乡。欲以钳制众口。使不得言其恶。吁亦甚矣。不特此也。顷者仁弘未及入城之前。有市民相聚偶语曰。恶人当朝。小民何以得生乎。仁弘之党为陈疏来京者。适过而听之。即自捉其人。而使邻人逢授。如法司禁乱知家之例。将待仁弘之入京。告以治罪云。市民哀乞数日。然后得免。都下藉藉。道路以目。是则欲移胁制岭南之习。而又将钳制辇毂之下也。臣闻谤议皇上者。亦不加罪。载于皇朝令甲。而我 殿下即位垂四十年。亦未闻有一人以语逼 圣躬被罪者。天子侯王。尚不敢以言己过失罪人。仁弘何人。乃敢以一言其过之故。使之祸延于一经其家之族属。一见其面之乡人。而至欲焚其一
门客杀人。解虽不杀。其实解杀之。遂罪郭解。今日仁弘之徒党。或为仁弘而任意黜人。或藉其势而擅杀士人。则仁弘乌得无罪乎。噫。使皋陶为士。则杀人之罪。虽天子之父。犹不得免。而况河浑辈。藉仁弘之势。杀人无忌。而人莫敢言。其可谓有国法乎。此辈之气势。崇长不已。则臣恐威福下移。而朝廷命令。不得行于岭南也。设令臣之所言。虚妄不实。而为仁弘者。果是善人。则当自反于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也。而乃移怒于族人。则至于黜乡。欲以钳制众口。使不得言其恶。吁亦甚矣。不特此也。顷者仁弘未及入城之前。有市民相聚偶语曰。恶人当朝。小民何以得生乎。仁弘之党为陈疏来京者。适过而听之。即自捉其人。而使邻人逢授。如法司禁乱知家之例。将待仁弘之入京。告以治罪云。市民哀乞数日。然后得免。都下藉藉。道路以目。是则欲移胁制岭南之习。而又将钳制辇毂之下也。臣闻谤议皇上者。亦不加罪。载于皇朝令甲。而我 殿下即位垂四十年。亦未闻有一人以语逼 圣躬被罪者。天子侯王。尚不敢以言己过失罪人。仁弘何人。乃敢以一言其过之故。使之祸延于一经其家之族属。一见其面之乡人。而至欲焚其一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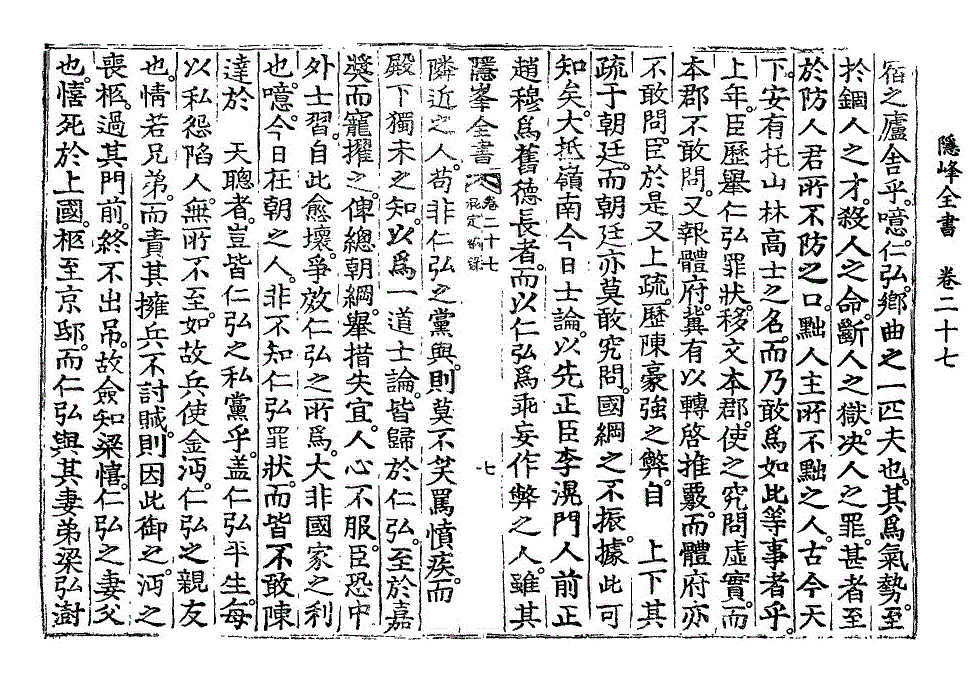 宿之庐舍乎。噫。仁弘。乡曲之一匹夫也。其为气势。至于锢人之才。杀人之命。断人之狱。决人之罪。甚者至于防人君所不防之口。黜人主所不黜之人。古今天下。安有托山林高士之名。而乃敢为如比等事者乎。上年。臣历举仁弘罪状。移文本郡。使之究问虚实。而本郡不敢问。又报体府。冀有以转启推覈。而体府亦不敢问。臣于是又上疏。历陈豪强之弊。自 上下其疏于朝廷。而朝廷亦莫敢究问。国纲之不振。据此可知矣。大抵岭南今日士论。以先正臣李滉门人前正赵穆为旧德长者。而以仁弘为乖妄作弊之人。虽其邻近之人。苟非仁弘之党与。则莫不笑骂愤疾。而 殿下独未之知。以为一道士论。皆归于仁弘。至于嘉奖而宠擢之。俾总朝纲。举措失宜。人心不服。臣恐中外士习。自此愈坏。争效仁弘之所为。大非国家之利也。噫。今日在朝之人。非不知仁弘罪状。而皆不敢陈达于 天聪者。岂皆仁弘之私党乎。盖仁弘平生。每以私怨陷人。无所不至。如故兵使金沔。仁弘之亲友也。情若兄弟。而责其拥兵不讨贼。则因此御之。沔之丧柩。过其门前。终不出吊。故佥知梁憘。仁弘之妻父也。憘死于上国。柩至京邸。而仁弘与其妻弟梁弘澍
宿之庐舍乎。噫。仁弘。乡曲之一匹夫也。其为气势。至于锢人之才。杀人之命。断人之狱。决人之罪。甚者至于防人君所不防之口。黜人主所不黜之人。古今天下。安有托山林高士之名。而乃敢为如比等事者乎。上年。臣历举仁弘罪状。移文本郡。使之究问虚实。而本郡不敢问。又报体府。冀有以转启推覈。而体府亦不敢问。臣于是又上疏。历陈豪强之弊。自 上下其疏于朝廷。而朝廷亦莫敢究问。国纲之不振。据此可知矣。大抵岭南今日士论。以先正臣李滉门人前正赵穆为旧德长者。而以仁弘为乖妄作弊之人。虽其邻近之人。苟非仁弘之党与。则莫不笑骂愤疾。而 殿下独未之知。以为一道士论。皆归于仁弘。至于嘉奖而宠擢之。俾总朝纲。举措失宜。人心不服。臣恐中外士习。自此愈坏。争效仁弘之所为。大非国家之利也。噫。今日在朝之人。非不知仁弘罪状。而皆不敢陈达于 天聪者。岂皆仁弘之私党乎。盖仁弘平生。每以私怨陷人。无所不至。如故兵使金沔。仁弘之亲友也。情若兄弟。而责其拥兵不讨贼。则因此御之。沔之丧柩。过其门前。终不出吊。故佥知梁憘。仁弘之妻父也。憘死于上国。柩至京邸。而仁弘与其妻弟梁弘澍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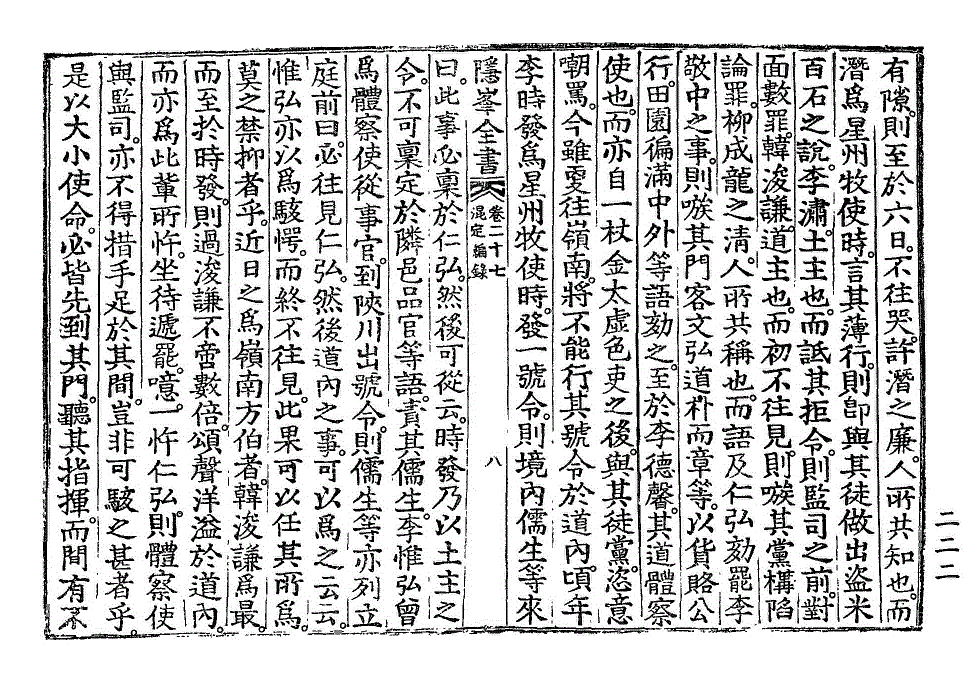 有隙。则至于六日。不往哭。许潜之廉。人所共知也。而潜为星州牧使时。言其薄行。则即与其徒做出盗米百石之说。李潚。土主也。而诋其拒令。则监司之前。对面数罪。韩浚谦。道主也。而初不往见。则嗾其党构陷论罪。柳成龙之清。人所共称也。而语及仁弘劾罢李敬中之事。则嗾其门客文弘道,朴而章等。以货赂公行。田园遍满中外等语劾之。至于李德馨。其道体察使也。而亦自一杖金太虚色吏之后。与其徒党。恣意嘲骂。今虽更往岭南。将不能行其号令于道内。顷年李时发为星州牧使时。发一号令。则境内儒生等来曰。此事必禀于仁弘。然后可从云。时发乃以土主之令。不可禀定于邻邑品官等语。责其儒生。李惟弘曾为体察使从事官。到陜川出号令。则儒生等亦列立庭前曰。必往见仁弘。然后道内之事。可以为之云云。惟弘亦以为骇愕。而终不往见。此果可以任其所为。莫之禁抑者乎。近日之为岭南方伯者。韩浚谦为最。而至于时发。则过浚谦不啻数倍。颂声洋溢于道内。而亦为此辈所忤。坐待递罢。噫。一忤仁弘。则体察使与监司。亦不得措手足于其间。岂非可骇之甚者乎。是以大小使命。必皆先到其门。听其指挥。而间有不
有隙。则至于六日。不往哭。许潜之廉。人所共知也。而潜为星州牧使时。言其薄行。则即与其徒做出盗米百石之说。李潚。土主也。而诋其拒令。则监司之前。对面数罪。韩浚谦。道主也。而初不往见。则嗾其党构陷论罪。柳成龙之清。人所共称也。而语及仁弘劾罢李敬中之事。则嗾其门客文弘道,朴而章等。以货赂公行。田园遍满中外等语劾之。至于李德馨。其道体察使也。而亦自一杖金太虚色吏之后。与其徒党。恣意嘲骂。今虽更往岭南。将不能行其号令于道内。顷年李时发为星州牧使时。发一号令。则境内儒生等来曰。此事必禀于仁弘。然后可从云。时发乃以土主之令。不可禀定于邻邑品官等语。责其儒生。李惟弘曾为体察使从事官。到陜川出号令。则儒生等亦列立庭前曰。必往见仁弘。然后道内之事。可以为之云云。惟弘亦以为骇愕。而终不往见。此果可以任其所为。莫之禁抑者乎。近日之为岭南方伯者。韩浚谦为最。而至于时发。则过浚谦不啻数倍。颂声洋溢于道内。而亦为此辈所忤。坐待递罢。噫。一忤仁弘。则体察使与监司。亦不得措手足于其间。岂非可骇之甚者乎。是以大小使命。必皆先到其门。听其指挥。而间有不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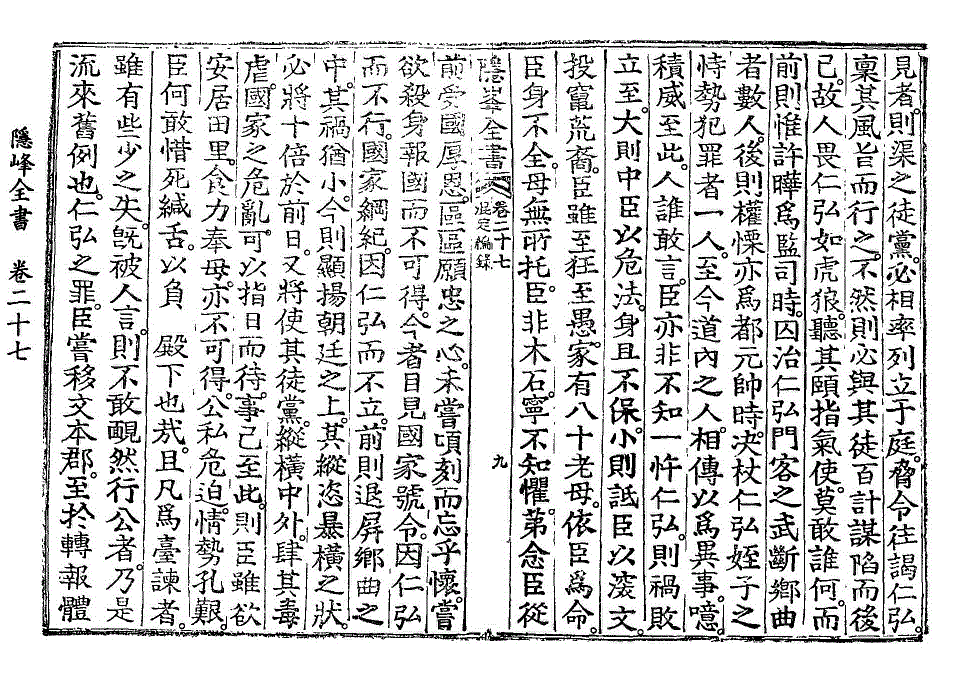 见者。则渠之徒党。必相率列立于庭。胁令往谒仁弘。禀其风旨而行之。不然则必与其徒百计谋陷而后已。故人畏仁弘如虎狼。听其颐指气使。莫敢谁何。而前则惟许晔为监司时。囚治仁弘门客之武断乡曲者数人。后则权慄亦为都元帅时。决杖仁弘侄子之恃势犯罪者一人。至今道内之人。相传以为异事。噫。积威至此。人谁敢言。臣亦非不知一忤仁弘。则祸败立至。大则中臣以危法。身且不保。小则诋臣以深文。投窜荒裔。臣虽至狂至愚。家有八十老母。依臣为命。臣身不全。母无所托。臣非木石。宁不知惧。第念臣从前受国厚恩。区区愿忠之心。未尝顷刻而忘乎怀。尝欲杀身报国而不可得。今者目见国家号令。因仁弘而不行。国家纲纪。因仁弘而不立。前则退屏乡曲之中。其祸犹小。今则显扬朝廷之上。其纵恣暴横之状。必将十倍于前日。又将使其徒党。纵横中外。肆其毒虐。国家之危乱。可以指日而待。事已至此。则臣虽欲安居田里。食力奉母。亦不可得。公私危迫。情势孔艰。臣何敢惜死缄舌。以负 殿下也哉。且凡为台谏者。虽有些少之失。既被人言。则不敢腼然行公者。乃是流来旧例也。仁弘之罪。臣尝移文本郡。至于转报体
见者。则渠之徒党。必相率列立于庭。胁令往谒仁弘。禀其风旨而行之。不然则必与其徒百计谋陷而后已。故人畏仁弘如虎狼。听其颐指气使。莫敢谁何。而前则惟许晔为监司时。囚治仁弘门客之武断乡曲者数人。后则权慄亦为都元帅时。决杖仁弘侄子之恃势犯罪者一人。至今道内之人。相传以为异事。噫。积威至此。人谁敢言。臣亦非不知一忤仁弘。则祸败立至。大则中臣以危法。身且不保。小则诋臣以深文。投窜荒裔。臣虽至狂至愚。家有八十老母。依臣为命。臣身不全。母无所托。臣非木石。宁不知惧。第念臣从前受国厚恩。区区愿忠之心。未尝顷刻而忘乎怀。尝欲杀身报国而不可得。今者目见国家号令。因仁弘而不行。国家纲纪。因仁弘而不立。前则退屏乡曲之中。其祸犹小。今则显扬朝廷之上。其纵恣暴横之状。必将十倍于前日。又将使其徒党。纵横中外。肆其毒虐。国家之危乱。可以指日而待。事已至此。则臣虽欲安居田里。食力奉母。亦不可得。公私危迫。情势孔艰。臣何敢惜死缄舌。以负 殿下也哉。且凡为台谏者。虽有些少之失。既被人言。则不敢腼然行公者。乃是流来旧例也。仁弘之罪。臣尝移文本郡。至于转报体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23L 页
 府。中外喧传。人皆闻知。而仁弘欲掩人之议己。终不避嫌。有若身无罪犯者然。呼唱道路。略无忌惮。其无朝廷蔑公论。可谓极矣。三司之官。亦非不知其无理。而或畏威不言。或党比曲护。无一人斥其失体者。终使殿下孤立于上。呜呼。小事且然。况其大者乎。臣所历举仁弘种种罪恶。若委之于人人之所共知而已。则亦或泛然。而其所听闻。皆有證验。伏望 殿下命召仁弘与臣。廷辨虚实。如 成庙朝旧事。万一臣之所言。果无实状。则臣当伏诬罔之典。以为谗人戒。但臣成浑之门生也。仁弘方以攻浑为事。此言发于臣口。或未免近于妒妇之言矣。然亦有所不然者。若以攻浑之故。为之愤疾。而必欲横加诋诬。则朴惺之攻浑。亦不下于仁弘。臣之所攻。不必在于惺而在于仁弘也。臣曾往岭南闻之。则攻浑之论。惺与仁弘一也。而惺则其豪强纵恣。无一事近于仁弘者。至于所见同异。不可谓之深咎。故臣之所以深恶痛疾者。在于仁弘。而至于移关本郡。推究其虚实。将以转报体府。欲惩其豪右之弊者也。况师友。以义而合者也。臣之所以事浑为师者。将以学是义也。如使成浑之罪。果如言者之论。则臣何敢曲护。上诬 圣明。而反攻仁弘
府。中外喧传。人皆闻知。而仁弘欲掩人之议己。终不避嫌。有若身无罪犯者然。呼唱道路。略无忌惮。其无朝廷蔑公论。可谓极矣。三司之官。亦非不知其无理。而或畏威不言。或党比曲护。无一人斥其失体者。终使殿下孤立于上。呜呼。小事且然。况其大者乎。臣所历举仁弘种种罪恶。若委之于人人之所共知而已。则亦或泛然。而其所听闻。皆有證验。伏望 殿下命召仁弘与臣。廷辨虚实。如 成庙朝旧事。万一臣之所言。果无实状。则臣当伏诬罔之典。以为谗人戒。但臣成浑之门生也。仁弘方以攻浑为事。此言发于臣口。或未免近于妒妇之言矣。然亦有所不然者。若以攻浑之故。为之愤疾。而必欲横加诋诬。则朴惺之攻浑。亦不下于仁弘。臣之所攻。不必在于惺而在于仁弘也。臣曾往岭南闻之。则攻浑之论。惺与仁弘一也。而惺则其豪强纵恣。无一事近于仁弘者。至于所见同异。不可谓之深咎。故臣之所以深恶痛疾者。在于仁弘。而至于移关本郡。推究其虚实。将以转报体府。欲惩其豪右之弊者也。况师友。以义而合者也。臣之所以事浑为师者。将以学是义也。如使成浑之罪。果如言者之论。则臣何敢曲护。上诬 圣明。而反攻仁弘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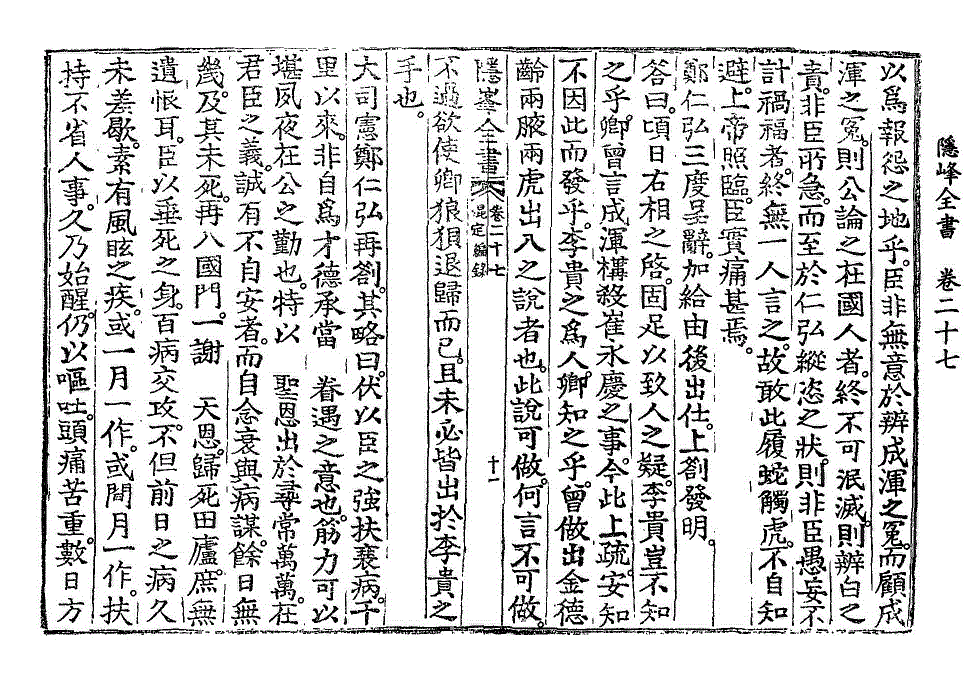 以为报怨之地乎。臣非无意于辨成浑之冤。而顾成浑之冤。则公论之在国人者。终不可泯灭。则辨白之责。非臣所急。而至于仁弘纵恣之状。则非臣愚妄不计祸福者。终无一人言之。故敢此履蛇触虎。不自知避。上帝照临。臣实痛甚焉。
以为报怨之地乎。臣非无意于辨成浑之冤。而顾成浑之冤。则公论之在国人者。终不可泯灭。则辨白之责。非臣所急。而至于仁弘纵恣之状。则非臣愚妄不计祸福者。终无一人言之。故敢此履蛇触虎。不自知避。上帝照临。臣实痛甚焉。郑仁弘三度呈辞。加给由后出仕。上劄发明。
答曰。顷日右相之启。固足以致人之疑。李贵岂不知之乎。卿曾言成浑构杀崔永庆之事。今此上疏。安知不因此而发乎。李贵之为人。卿知之乎。曾做出金德龄两腋两虎出入之说者也。此说可做。何言不可做。不过欲使卿狼狈退归而已。且未必皆出于李贵之手也。
大司宪郑仁弘再劄。其略曰。伏以臣之强扶衰病。千里以来。非自为才德承当 眷遇之意也。筋力可以堪夙夜在公之勤也。特以 圣恩出于寻常万万。在君臣之义。诚有不自安者。而自念衰与病谋。馀日无几。及其未死。再入国门。一谢 天恩。归死田庐。庶无遗恨耳。臣以垂死之身。百病交攻。不但前日之病久未差歇。素有风眩之疾。或一月一作。或间月一作。扶持不省人事。久乃始醒。仍以呕吐。头痛苦重。数日方
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24L 页
 定。自近日来。或间日而作。或连日而发。其势转重。近于丑恶之疾。但不至投水而入火耳。身病如此。其不可仕一也。臣闻四十而强仕。七十而致仕。后之仕者。虽不能尽然。然此诚士大夫止仕之大閒。盖以年至七十。筋力衰乏。志虑眊瞆。则命德名位。决不可冒据故也。况臣非徒牛马之齿迟暮已甚。获罪于天。丧亡祸酷。十馀年间。父母兄弟妻子相继见背。无虑十馀人。悲痛哭泣之馀。目视昏昧而文字不能省阅。书狎不见毫末。精神耗竭而视听艰涩。转头忘失。凡举止之际。耄荒瘦顿之状。有不可一一言者。而乃以致仕之年。反为强仕之日。不亦难乎。虽欲自列于庶官之末。犹为可羞。况风宪之职乎。犹复强颜冒处。则廉耻已丧。风节先坠。环顾一身。更无可观。外被人讥。内愧于心。欲以此纠他人之失。正朝廷之非。正所谓手援天下者也。其不可仕二也。臣伏见李贵之疏。历举臣罪。辄引缙绅之士。皆有所据。其在疏中者。宜亦见闻。岂是无根构捏之言也。至于领议政李德馨之言曰。郑仁弘以士自名。不可轻易处之等语。亦非贵之言为不实也。特以无状之身。窃取虚名。托迹士类。故言不可轻易下手。以致其害云耳。其馀许多说话。皆有
定。自近日来。或间日而作。或连日而发。其势转重。近于丑恶之疾。但不至投水而入火耳。身病如此。其不可仕一也。臣闻四十而强仕。七十而致仕。后之仕者。虽不能尽然。然此诚士大夫止仕之大閒。盖以年至七十。筋力衰乏。志虑眊瞆。则命德名位。决不可冒据故也。况臣非徒牛马之齿迟暮已甚。获罪于天。丧亡祸酷。十馀年间。父母兄弟妻子相继见背。无虑十馀人。悲痛哭泣之馀。目视昏昧而文字不能省阅。书狎不见毫末。精神耗竭而视听艰涩。转头忘失。凡举止之际。耄荒瘦顿之状。有不可一一言者。而乃以致仕之年。反为强仕之日。不亦难乎。虽欲自列于庶官之末。犹为可羞。况风宪之职乎。犹复强颜冒处。则廉耻已丧。风节先坠。环顾一身。更无可观。外被人讥。内愧于心。欲以此纠他人之失。正朝廷之非。正所谓手援天下者也。其不可仕二也。臣伏见李贵之疏。历举臣罪。辄引缙绅之士。皆有所据。其在疏中者。宜亦见闻。岂是无根构捏之言也。至于领议政李德馨之言曰。郑仁弘以士自名。不可轻易处之等语。亦非贵之言为不实也。特以无状之身。窃取虚名。托迹士类。故言不可轻易下手。以致其害云耳。其馀许多说话。皆有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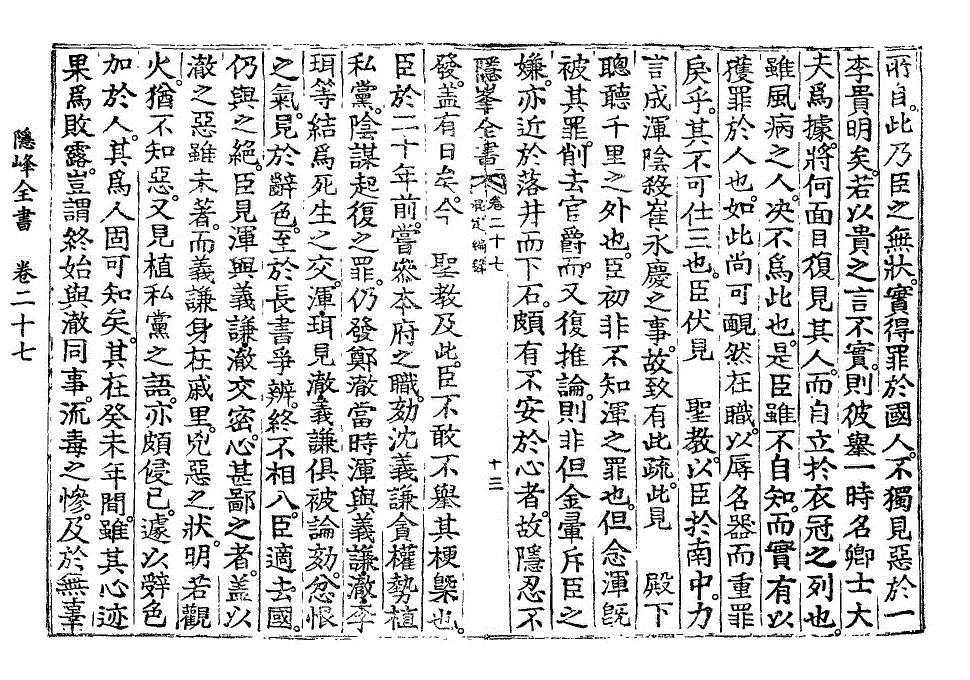 所自。此乃臣之无状。实得罪于国人。不独见恶于一李贵明矣。若以贵之言不实。则彼举一时名卿士大夫为据。将何面目复见其人。而自立于衣冠之列也。虽风病之人。决不为此也。是臣虽不自知。而实有以获罪于人也。如此尚可腼然在职。以辱名器而重罪戾乎。其不可仕三也。臣伏见 圣教。以臣于南中。力言成浑阴杀崔永庆之事。故致有此疏。此见 殿下聪听千里之外也。臣初非不知浑之罪也。但念浑既被其罪。削去官爵。而又复推论。则非但金晕斥臣之嫌。亦近于落井而下石。颇有不安于心者。故隐忍不发。盖有日矣。今 圣教及此。臣不敢不举其梗槩也。臣于二十年前。尝参本府之职。劾沈义谦贪权势植私党。阴谋起复之罪。仍发郑澈当时浑与义谦,澈,李珥等结为死生之交。浑,珥见澈,义谦俱被论劾。忿恨之气。见于辞色。至于长书争辨。终不相入。臣适去国。仍与之绝。臣见浑与义谦,澈交密。心甚鄙之者。盖以澈之恶虽未著。而义谦身在戚里。凶恶之状。明若观火。犹不知恶。又见植私党之语。亦颇侵己。遽以辞色加于人。其为人固可知矣。其在癸未年间。虽其心迹果为败露。岂谓终始与澈同事。流毒之惨。及于无辜
所自。此乃臣之无状。实得罪于国人。不独见恶于一李贵明矣。若以贵之言不实。则彼举一时名卿士大夫为据。将何面目复见其人。而自立于衣冠之列也。虽风病之人。决不为此也。是臣虽不自知。而实有以获罪于人也。如此尚可腼然在职。以辱名器而重罪戾乎。其不可仕三也。臣伏见 圣教。以臣于南中。力言成浑阴杀崔永庆之事。故致有此疏。此见 殿下聪听千里之外也。臣初非不知浑之罪也。但念浑既被其罪。削去官爵。而又复推论。则非但金晕斥臣之嫌。亦近于落井而下石。颇有不安于心者。故隐忍不发。盖有日矣。今 圣教及此。臣不敢不举其梗槩也。臣于二十年前。尝参本府之职。劾沈义谦贪权势植私党。阴谋起复之罪。仍发郑澈当时浑与义谦,澈,李珥等结为死生之交。浑,珥见澈,义谦俱被论劾。忿恨之气。见于辞色。至于长书争辨。终不相入。臣适去国。仍与之绝。臣见浑与义谦,澈交密。心甚鄙之者。盖以澈之恶虽未著。而义谦身在戚里。凶恶之状。明若观火。犹不知恶。又见植私党之语。亦颇侵己。遽以辞色加于人。其为人固可知矣。其在癸未年间。虽其心迹果为败露。岂谓终始与澈同事。流毒之惨。及于无辜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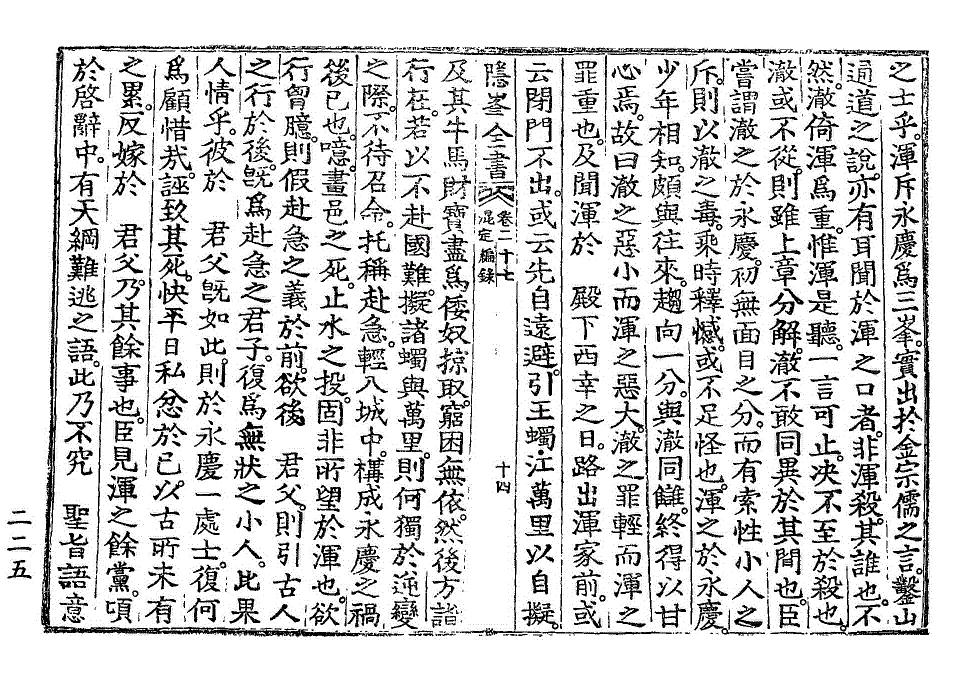 之士乎。浑斥永庆为三峰。实出于金宗儒之言。凿山通道之说。亦有耳闻于浑之口者。非浑杀。其谁也。不然。澈倚浑为重。惟浑是听。一言可止。决不至于杀也。澈或不从。则虽上章分解。澈不敢同异于其间也。臣尝谓澈之于永庆。初无面目之分。而有索性小人之斥。则以澈之毒。乘时释憾。或不足怪也。浑之于永庆。少年相知。颇与往来。趋向一分。与澈同雠。终得以甘心焉。故曰澈之恶小而浑之恶大。澈之罪轻而浑之罪重也。及闻浑于 殿下西幸之日。路出浑家前。或云闭门不出。或云先自远避。引王蠋,江万里以自拟。及其牛马财宝尽为倭奴掠取。穷困无依。然后方诣行在。若以不赴国难。拟诸蠋与万里。则何独于逆变之际。不待召命。托称赴急。轻入城中。构成永庆之祸后已也。噫。画邑之死。止水之投。固非所望于浑也。欲行胸臆。则假赴急之义于前。欲后 君父。则引古人之行于后。既为赴急之君子。复为无状之小人。此果人情乎。彼于 君父既如此。则于永庆一处士。复何为顾惜哉。诬致其死。快平日私忿于己。以古所未有之累。反嫁于 君父。乃其馀事也。臣见浑之馀党。顷于启辞中。有天纲(一作网)难逃之语。此乃不究 圣旨语意
之士乎。浑斥永庆为三峰。实出于金宗儒之言。凿山通道之说。亦有耳闻于浑之口者。非浑杀。其谁也。不然。澈倚浑为重。惟浑是听。一言可止。决不至于杀也。澈或不从。则虽上章分解。澈不敢同异于其间也。臣尝谓澈之于永庆。初无面目之分。而有索性小人之斥。则以澈之毒。乘时释憾。或不足怪也。浑之于永庆。少年相知。颇与往来。趋向一分。与澈同雠。终得以甘心焉。故曰澈之恶小而浑之恶大。澈之罪轻而浑之罪重也。及闻浑于 殿下西幸之日。路出浑家前。或云闭门不出。或云先自远避。引王蠋,江万里以自拟。及其牛马财宝尽为倭奴掠取。穷困无依。然后方诣行在。若以不赴国难。拟诸蠋与万里。则何独于逆变之际。不待召命。托称赴急。轻入城中。构成永庆之祸后已也。噫。画邑之死。止水之投。固非所望于浑也。欲行胸臆。则假赴急之义于前。欲后 君父。则引古人之行于后。既为赴急之君子。复为无状之小人。此果人情乎。彼于 君父既如此。则于永庆一处士。复何为顾惜哉。诬致其死。快平日私忿于己。以古所未有之累。反嫁于 君父。乃其馀事也。臣见浑之馀党。顷于启辞中。有天纲(一作网)难逃之语。此乃不究 圣旨语意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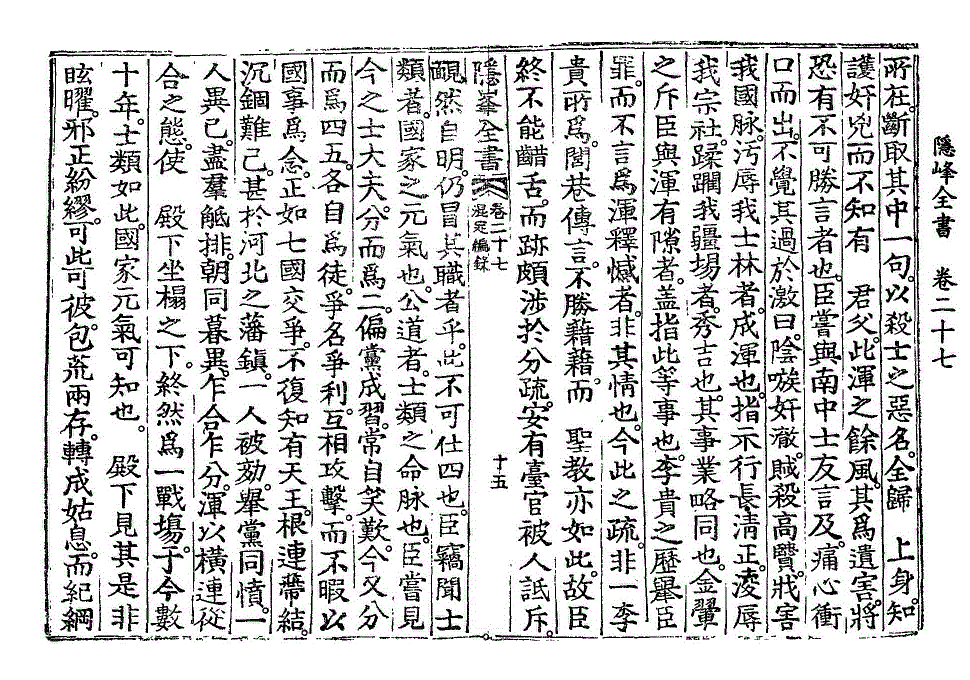 所在。断取其中一句。以杀士之恶名。全归 上身。知护奸凶而不知有 君父。此浑之馀风。其为遗害。将恐有不可胜言者也。臣尝与南中士友言及。痛心冲口而出。不觉其过于激曰。阴嗾奸澈。贼杀高贤。戕害我国脉。污辱我士林者。成浑也。指示行长,清正。凌辱我宗社。蹂躏我疆埸者。秀吉也。其事业略同也。金翚之斥臣与浑有隙者。盖指此等事也。李贵之历举臣罪。而不言为浑释憾者。非其情也。今此之疏。非一李贵所为。闾巷传言。不胜藉藉。而 圣教亦如此。故臣终不能齰舌。而迹颇涉于分疏。安有台官被人诋斥。腼然自明。仍冒其职者乎。此不可仕四也。臣窃闻士类者。国家之元气也。公道者。士类之命脉也。臣尝见今之士大夫。分而为二。偏党成习。常自笑叹。今又分而为四五。各自为徒。争名争利。互相攻击。而不暇以国事为念。正如七国交争。不复知有天王。根连蒂结。沈锢难已。甚于河北之藩镇。一人被劾。举党同愤。一人异己。尽群抵排。朝同暮异。乍合乍分。浑以横连从合之态。使 殿下坐榻之下。终然为一战场。于今数十年。士类如此。国家元气可知也。 殿下见其是非眩曜。邪正纷缪。可此可彼。包荒两存。转成姑息。而纪纲
所在。断取其中一句。以杀士之恶名。全归 上身。知护奸凶而不知有 君父。此浑之馀风。其为遗害。将恐有不可胜言者也。臣尝与南中士友言及。痛心冲口而出。不觉其过于激曰。阴嗾奸澈。贼杀高贤。戕害我国脉。污辱我士林者。成浑也。指示行长,清正。凌辱我宗社。蹂躏我疆埸者。秀吉也。其事业略同也。金翚之斥臣与浑有隙者。盖指此等事也。李贵之历举臣罪。而不言为浑释憾者。非其情也。今此之疏。非一李贵所为。闾巷传言。不胜藉藉。而 圣教亦如此。故臣终不能齰舌。而迹颇涉于分疏。安有台官被人诋斥。腼然自明。仍冒其职者乎。此不可仕四也。臣窃闻士类者。国家之元气也。公道者。士类之命脉也。臣尝见今之士大夫。分而为二。偏党成习。常自笑叹。今又分而为四五。各自为徒。争名争利。互相攻击。而不暇以国事为念。正如七国交争。不复知有天王。根连蒂结。沈锢难已。甚于河北之藩镇。一人被劾。举党同愤。一人异己。尽群抵排。朝同暮异。乍合乍分。浑以横连从合之态。使 殿下坐榻之下。终然为一战场。于今数十年。士类如此。国家元气可知也。 殿下见其是非眩曜。邪正纷缪。可此可彼。包荒两存。转成姑息。而纪纲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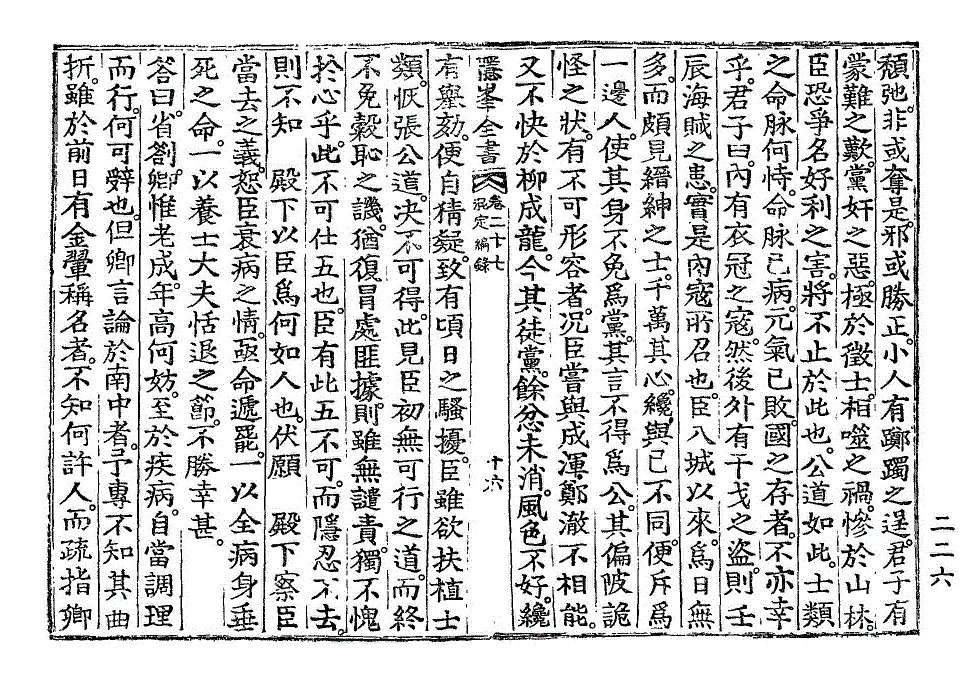 颓弛。非或夺是。邪或胜正。小人有踯躅之逞。君子有蒙难之叹。党奸之恶。极于徵士。相噬之祸。惨于山林。臣恐争名好利之害。将不止于此也。公道如此。士类之命脉何恃。命脉已病。元气已败。国之存者。不亦幸乎。君子曰。内有衣冠之寇。然后外有干戈之盗。则壬辰海贼之患。实是内寇所召也。臣入城以来。为日无多。而颇见缙绅之士。千万其心。才与己不同。便斥为一边人。使其身不免为党。其言不得为公。其偏陂诡怪之状。有不可形容者。况臣尝与成浑,郑澈不相能。又不快于柳成龙。今其徒党。馀忿未消。风色不好。才有举劾。便自猜疑。致有顷日之骚扰。臣虽欲扶植士类。恢张公道。决不可得。此见臣初无可行之道。而终不免谷耻之讥。犹复冒处匪据。则虽无谴责。独不愧于心乎。此不可仕五也。臣有此五不可。而隐忍不去。则不知 殿下以臣为何如人也。伏愿 殿下察臣当去之义。恕臣衰病之情。亟命递罢。一以全病身垂死之命。一以养士大夫恬退之节。不胜幸甚。
颓弛。非或夺是。邪或胜正。小人有踯躅之逞。君子有蒙难之叹。党奸之恶。极于徵士。相噬之祸。惨于山林。臣恐争名好利之害。将不止于此也。公道如此。士类之命脉何恃。命脉已病。元气已败。国之存者。不亦幸乎。君子曰。内有衣冠之寇。然后外有干戈之盗。则壬辰海贼之患。实是内寇所召也。臣入城以来。为日无多。而颇见缙绅之士。千万其心。才与己不同。便斥为一边人。使其身不免为党。其言不得为公。其偏陂诡怪之状。有不可形容者。况臣尝与成浑,郑澈不相能。又不快于柳成龙。今其徒党。馀忿未消。风色不好。才有举劾。便自猜疑。致有顷日之骚扰。臣虽欲扶植士类。恢张公道。决不可得。此见臣初无可行之道。而终不免谷耻之讥。犹复冒处匪据。则虽无谴责。独不愧于心乎。此不可仕五也。臣有此五不可。而隐忍不去。则不知 殿下以臣为何如人也。伏愿 殿下察臣当去之义。恕臣衰病之情。亟命递罢。一以全病身垂死之命。一以养士大夫恬退之节。不胜幸甚。答曰。省劄。卿惟老成。年高何妨。至于疾病。自当调理而行。何可辞也。但卿言论于南中者。予专不知其曲折。虽于前日有金翚称名者。不知何许人。而疏指卿
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27H 页
 名。将有欲害之渐。又见李贵之疏。显加卿以不测之名。予疑其为奸人所为。今见劄辞。果知致人多口之有其由也。自古忠贤之致人多口何限。不足数也。亦不足介怀也。卿宜勿辞。更加尽心补予。
名。将有欲害之渐。又见李贵之疏。显加卿以不测之名。予疑其为奸人所为。今见劄辞。果知致人多口之有其由也。自古忠贤之致人多口何限。不足数也。亦不足介怀也。卿宜勿辞。更加尽心补予。传曰。崔永庆弟馀庆赠职。 赠户曹参议。吏曹 启曰。馀庆之子奉永庆祀者。方在都下。而不堪饥馁云。相当职除授何如。
答曰。依允。后日政。崔弘言社稷参奉文景虎。松罗察访除授。 府 启曰。吏曹佐郎洪瑞凤。放黜未久。还叙与无罪者同。翰林金瑬。以复雠从事官。忘父之雠。惟事酒色。请罢事。
大提学李廷龟。三度辞劄。
司谏郑㷤避嫌 启曰。臣伏见大司宪郑仁弘劄辞。其形容今之士大夫之弊习者。正中时病也。但观其臣尝与成浑,郑澈不相能。又不快于柳成龙。今其徒党。馀忿未消。风色不好。才有论劾。便自猜疑。致有顷日之骚扰云。未知只据仁弘自为李贵所斥而言之也。其中才有论劾。便自猜疑。致有顷日之骚扰等语。似指顷日论尹承勋事也。其时臣为司谏。不欲论承勋者。非有他意。论大臣不可轻易。是不过重朝廷之
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27L 页
 意。以言语之失。论劾大臣之为不得中。至于两司俱发。尤为未安。臣言实出于公心。非有所偏私也。台谏以一事被递。未久还授。又不为更引前嫌。臣亦知其流来成事。今不必再欲烦渎于 圣聪。而但仁弘遭不时遇。起于山林。则其担当清议。恢张公道。孰不想望。而顷日骚扰一事。又在其五不可仕之一。夫士君子于大是非。则当初冰炭水火之不能同。固不可以苟合。其馀可否相济之事。虽有些少不合。不必执以为相疑。此固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之道。若仁弘实不能泰然于顷日之事。有此说话。则顷日之事。臣实发端。而不可以臣十辈换一仁弘。此臣所以不敢不以区区之意。自劾于 圣明之前也。臣之事势如此。决难仍冒。请 命罢斥臣职。一以安仁弘之心。一以慰士类之望。
意。以言语之失。论劾大臣之为不得中。至于两司俱发。尤为未安。臣言实出于公心。非有所偏私也。台谏以一事被递。未久还授。又不为更引前嫌。臣亦知其流来成事。今不必再欲烦渎于 圣聪。而但仁弘遭不时遇。起于山林。则其担当清议。恢张公道。孰不想望。而顷日骚扰一事。又在其五不可仕之一。夫士君子于大是非。则当初冰炭水火之不能同。固不可以苟合。其馀可否相济之事。虽有些少不合。不必执以为相疑。此固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之道。若仁弘实不能泰然于顷日之事。有此说话。则顷日之事。臣实发端。而不可以臣十辈换一仁弘。此臣所以不敢不以区区之意。自劾于 圣明之前也。臣之事势如此。决难仍冒。请 命罢斥臣职。一以安仁弘之心。一以慰士类之望。答曰。勿辞。退待物论。谏院处置郑㷤。递差。
执义文励避嫌 启曰。臣猥以寒贱。滥叨宠权。所当星夜骏奔。驰谢不暇。而素患风湿。又得疝痛。久稽旬朔。方俟诛夷。而不意亚长之命。更加无似之身。任重责大。尤非庸者所堪。惊惶罔措。战慄无地。臣窃闻李贵。捏造无根之言。构陷仁弘。无所不至。其为设心。极
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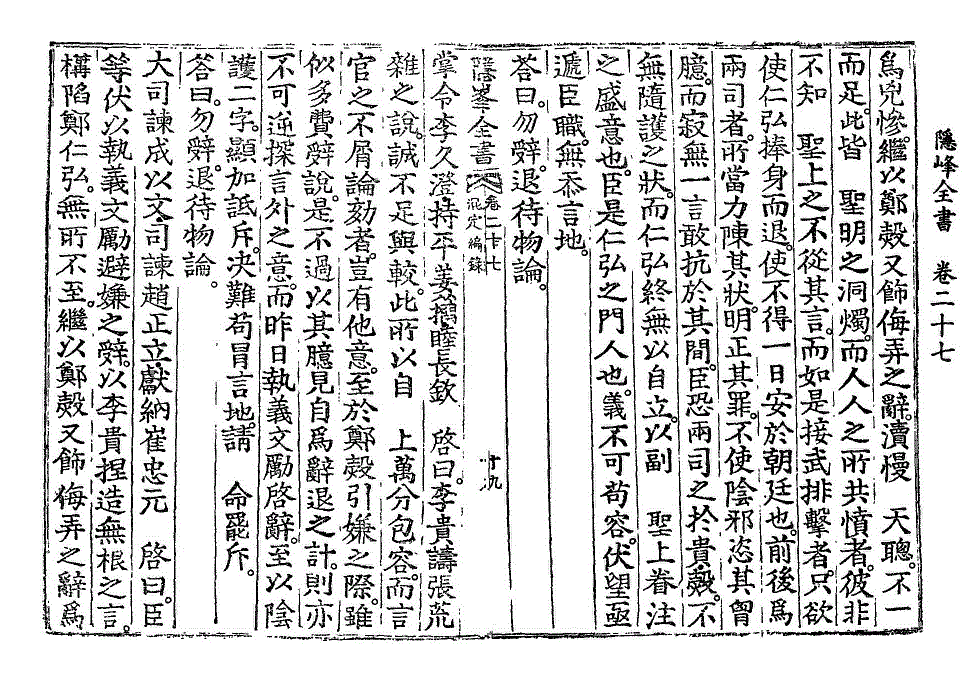 为凶惨。继以郑㷤又饰侮弄之辞。渎慢 天聪。不一而足。此皆 圣明之洞烛。而人人之所共愤者。彼非不知 圣上之不从其言。而如是接武排击者。只欲使仁弘捧身而退。使不得一日安于朝廷也。前后为两司者。所当力陈其状。明正其罪。不使阴邪恣其胸臆。而寂无一言敢抗于其间。臣恐两司之于贵,㷤。不无随护之状。而仁弘终无以自立。以副 圣上眷注之盛意也。臣是仁弘之门人也。义不可苟容。伏望亟递臣职。无忝言地。
为凶惨。继以郑㷤又饰侮弄之辞。渎慢 天聪。不一而足。此皆 圣明之洞烛。而人人之所共愤者。彼非不知 圣上之不从其言。而如是接武排击者。只欲使仁弘捧身而退。使不得一日安于朝廷也。前后为两司者。所当力陈其状。明正其罪。不使阴邪恣其胸臆。而寂无一言敢抗于其间。臣恐两司之于贵,㷤。不无随护之状。而仁弘终无以自立。以副 圣上眷注之盛意也。臣是仁弘之门人也。义不可苟容。伏望亟递臣职。无忝言地。答曰。勿辞。退待物论。
掌令李久澄,持平姜籀,睦长钦 启曰。李贵诪张荒杂之说。诚不足与较。此所以自 上万分包容。而言官之不屑论劾者。岂有他意。至于郑㷤引嫌之际。虽似多费辞说。是不过以其臆见自为辞退之计。则亦不可逆探言外之意。而昨日执义文励启辞。至以阴护二字。显加诋斥。决难苟冒言地。请 命罢斥。
答曰。勿辞。退待物论。
大司谏成以文,司谏赵正立,献纳崔忠元 启曰。臣等伏以执义文励避嫌之辞。以李贵捏造无根之言。构陷郑仁弘。无所不至。继以郑㷤又饰侮弄之辞为
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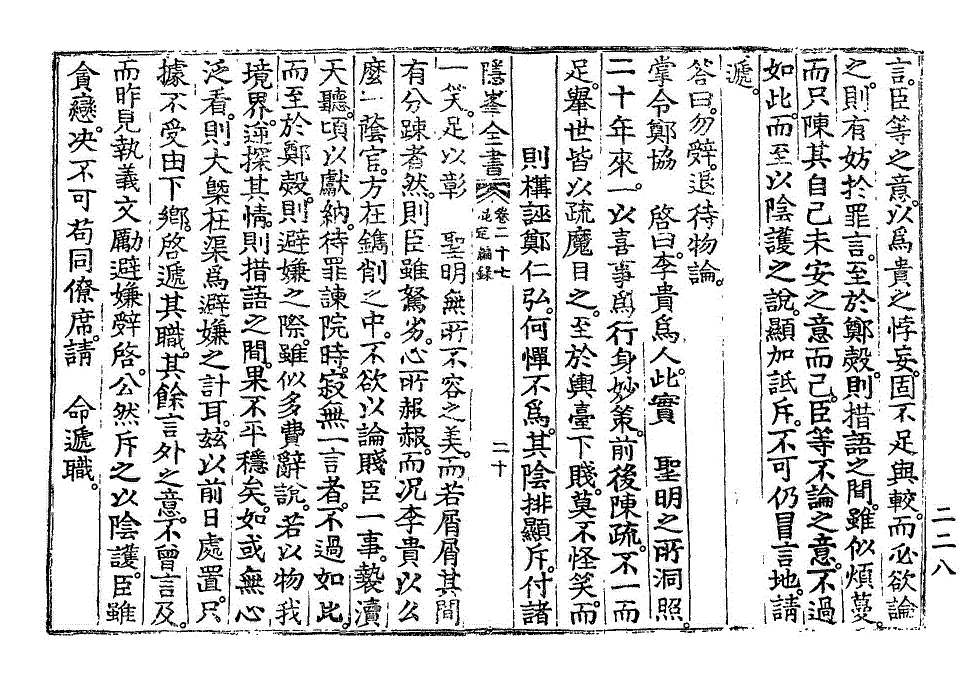 言。臣等之意。以为贵之悖妄。固不足与较。而必欲论之。则有妨于罪言。至于郑㷤。则措语之间。虽似烦蔓。而只陈其自己未安之意而已。臣等不论之意。不过如此。而至以阴护之说。显加诋斥。不可仍冒言地。请递。
言。臣等之意。以为贵之悖妄。固不足与较。而必欲论之。则有妨于罪言。至于郑㷤。则措语之间。虽似烦蔓。而只陈其自己未安之意而已。臣等不论之意。不过如此。而至以阴护之说。显加诋斥。不可仍冒言地。请递。答曰。勿辞。退待物论。
掌令郑协 启曰。李贵为人。此实 圣明之所洞照。二十年来。一以喜事为行身妙策。前后陈疏。不一而足。举世皆以疏魔目之。至于舆台下贱。莫不怪笑。而▣▣▣则构诬郑仁弘。何惮不为。其阴排显斥。付诸一笑。足以彰 圣明无所不容之美。而若屑屑其间有分疏者然。则臣虽驽劣。心所赧赧。而况李贵以幺么一荫官。方在镌削之中。不欲以论贱臣一事。褺渎天听。顷以献纳。待罪谏院时。寂无一言者。不过如此。而至于郑㷤。则避嫌之际。虽似多费辞说。若以物我境界。逆探其情。则措语之间。果不平稳矣。如或无心泛看。则大槩在渠为避嫌之计耳。玆以前日处置。只据不受由下乡。启递其职。其馀言外之意。不曾言及。而昨见执义文励避嫌辞启。公然斥之以阴护。臣虽贪恋。决不可苟同僚席。请 命递职。
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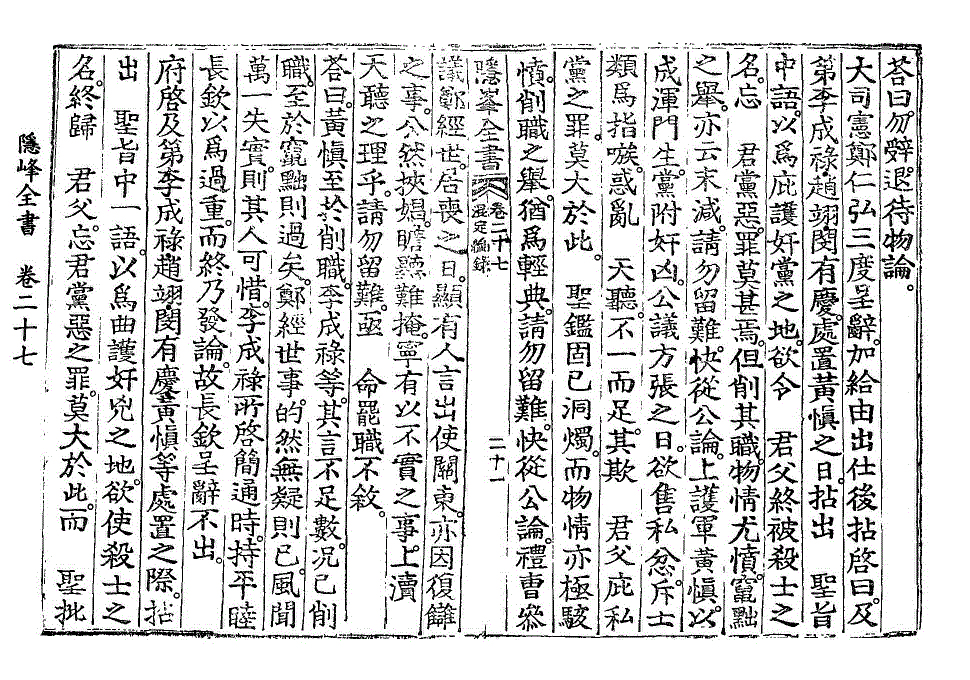 答曰。勿辞。退待物论。
答曰。勿辞。退待物论。大司宪郑仁弘三度呈辞。加给由出仕后拈启曰。及第李成禄,赵翊,闵有庆。处置黄慎之日。拈出 圣旨中语。以为庇护奸党之地。欲令 君父终被杀士之名。忘 君党恶。罪莫甚焉。但削其职。物情尤愤。窜黜之举。亦云末减。请勿留难。快从公论。上护军黄慎。以成浑门生。党附奸凶。公议方张之日。欲售私忿。斥士类为指嗾。惑乱 天听。不一而足。其欺 君父庇私党之罪。莫大于此。 圣鉴固已洞烛。而物情亦极骇愤。削职之举。犹为轻典。请勿留难。快从公论。礼曹参议郑经世。居丧之日。显有人言出使关东。亦因复雠之事。公然挟娼。瞻听难掩。宁有以不实之事。上渎 天听之理乎。请勿留难。亟 命罢职不叙。
答曰。黄慎至于削职。李成禄等。其言不足数。况已削职。至于窜黜则过矣。郑经世事。的然无疑则已。风闻万一失实。则其人可惜。李成禄所启简通时。持平睦长钦以为过重。而终乃发论。故长钦呈辞不出。
府启及第李成禄,赵翊,闵有庆,黄慎等处置之际。拈出 圣旨中一语。以为曲护奸凶之地。欲使杀士之名。终归 君父。忘君党恶之罪。莫大于此。而 圣批
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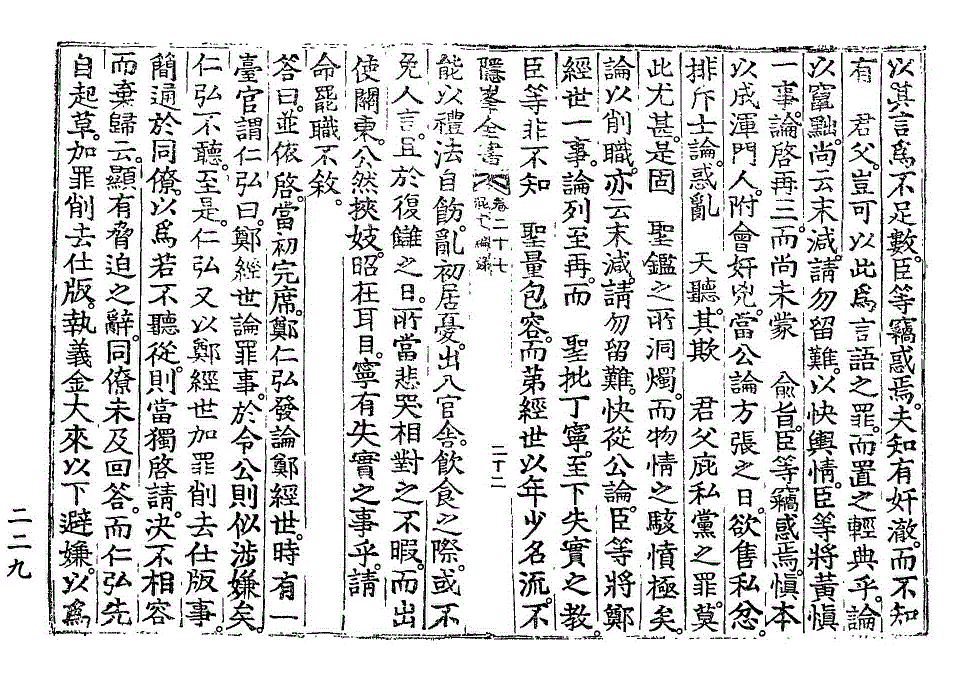 以其言为不足数。臣等窃惑焉。夫知有奸澈。而不知有 君父。岂可以此为言语之罪。而置之轻典乎。论以窜黜。尚云末减。请勿留难。以快舆情。臣等将黄慎一事。论启再三。而尚未蒙 俞旨。臣等窃惑焉。慎本以成浑门人。附会奸凶。当公论方张之日。欲售私忿。排斥士论。惑乱 天听。其欺 君父庇私党之罪。莫此尤甚。是固 圣鉴之所洞烛。而物情之骇愤极矣。论以削职。亦云末减。请勿留难。快从公论。臣等将郑经世一事。论列至再。而 圣批丁宁。至下失实之教。臣等非不知 圣量包容。而第经世以年少名流。不能以礼法自饬。乱初居忧。出入官舍。饮食之际。或不免人言。且于复雠之日。所当悲哭相对之不暇。而出使关东。公然挟妓。昭在耳目。宁有失实之事乎。请 命罢职不叙。
以其言为不足数。臣等窃惑焉。夫知有奸澈。而不知有 君父。岂可以此为言语之罪。而置之轻典乎。论以窜黜。尚云末减。请勿留难。以快舆情。臣等将黄慎一事。论启再三。而尚未蒙 俞旨。臣等窃惑焉。慎本以成浑门人。附会奸凶。当公论方张之日。欲售私忿。排斥士论。惑乱 天听。其欺 君父庇私党之罪。莫此尤甚。是固 圣鉴之所洞烛。而物情之骇愤极矣。论以削职。亦云末减。请勿留难。快从公论。臣等将郑经世一事。论列至再。而 圣批丁宁。至下失实之教。臣等非不知 圣量包容。而第经世以年少名流。不能以礼法自饬。乱初居忧。出入官舍。饮食之际。或不免人言。且于复雠之日。所当悲哭相对之不暇。而出使关东。公然挟妓。昭在耳目。宁有失实之事乎。请 命罢职不叙。答曰。并依启。当初完席。郑仁弘发论郑经世。时有一台官谓仁弘曰。郑经世论罪事。于令公则似涉嫌矣。仁弘不听。至是。仁弘又以郑经世加罪削去仕版事。简通于同僚。以为若不听从。则当独启请。决不相容而弃归云。显有胁迫之辞。同僚未及回答。而仁弘先自起草。加罪削去仕版。执义金大来以下避嫌。以为
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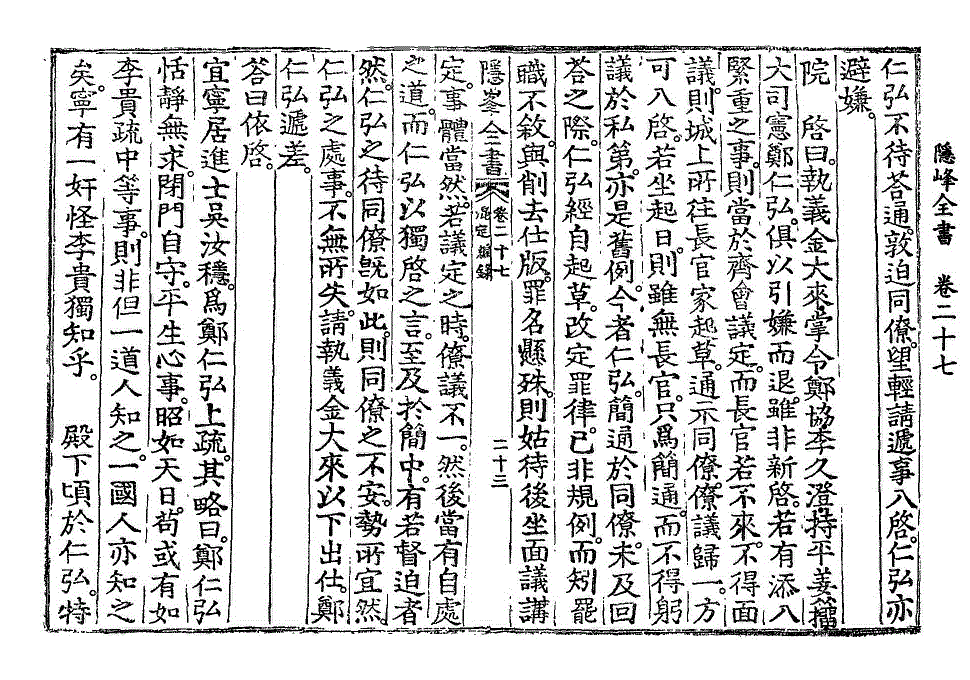 仁弘不待答通。敦迫同僚。望轻请递事入启。仁弘亦避嫌。
仁弘不待答通。敦迫同僚。望轻请递事入启。仁弘亦避嫌。院 启曰。执义金大来,掌令郑协,李久澄,持平姜籀,大司宪郑仁弘。俱以引嫌而退。虽非新启。若有添入紧重之事。则当于齐会议定。而长官若不来。不得面议。则城上所往长官家起草。通示同僚。僚议归一。方可入启。若坐起日。则虽无长官。只为简通。而不得躬议于私第。亦是旧例。今者仁弘。简通于同僚。未及回答之际。仁弘经自起草。改定罪律。已非规例。而矧罢职不叙。与削去仕版。罪召悬殊。则姑待后坐面议讲定。事体当然。若议定之时。僚议不一。然后当有自处之道。而仁弘以独启之言。至及于简中。有若督迫者然。仁弘之待同僚既如此。则同僚之不安。势所宜然。仁弘之处事。不无所失。请执义金大来以下出仕。郑仁弘递差。
答曰依启。
宜宁居进士吴汝稳。为郑仁弘上疏。其略曰。郑仁弘恬静无求。闭门自守。平生心事。昭如天日。苟或有如李贵疏中等事。则非但一道人知之。一国人亦知之矣。宁有一奸怪李贵独知乎。 殿下顷于仁弘。特
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30L 页
 加擢用。置诸宪长。则 殿下之真知仁弘明矣。至于李贵之疏。尚宽诬陷之典。是虽天地包荒之量。而窃恐媢嫉挤陷之徒。将自此益肆也。臣请粗言仁弘之行事。如实 殿下之真知。然后以及李贵之奸状可乎。仁弘学问之渊深。践履之笃实。非臣末学所可容测。而所性忠义。所守刚方。贫病为徒。绝意人事久矣。壬辰之变。关方一溃。屏翰失依。首唱乡兵。召募义旅。走檄列邑。誓天讨贼。使江右数百里之地。赖以获全。不特此也。义气壁立。砥柱颓波。故岭南人纪。以之不坠。不然则其能免卉服之乡乎。臣以为仁弘隐然有驱猛兽攘夷狄之功矣。贵也何人。乃敢罗织显斥至此。而 殿下置之不问。若俱收并蓄然。是是非非。果如是乎。贤贤恶恶。果如是乎。此臣之所未解也。臣窃见李贵等上年十月。以体察使李德馨召募官。行过居昌。文移陜川。条列仁弘罪目。以一道中士子之停举。守令之黜陟。狱讼流杀之处决。皆出于仁弘之手。又以拥兵七年。营私纵恣等语。令本郡守李馪推问牒报。其惹起衅端。网打士林之计。惨矣。凡有血气。莫不愤惋。而旋念贵亦妄人也已。不足与较。及仁弘承命赴阙。曾未浃辰。贵又上疏。敢仍前语。益肆阴凶。其
加擢用。置诸宪长。则 殿下之真知仁弘明矣。至于李贵之疏。尚宽诬陷之典。是虽天地包荒之量。而窃恐媢嫉挤陷之徒。将自此益肆也。臣请粗言仁弘之行事。如实 殿下之真知。然后以及李贵之奸状可乎。仁弘学问之渊深。践履之笃实。非臣末学所可容测。而所性忠义。所守刚方。贫病为徒。绝意人事久矣。壬辰之变。关方一溃。屏翰失依。首唱乡兵。召募义旅。走檄列邑。誓天讨贼。使江右数百里之地。赖以获全。不特此也。义气壁立。砥柱颓波。故岭南人纪。以之不坠。不然则其能免卉服之乡乎。臣以为仁弘隐然有驱猛兽攘夷狄之功矣。贵也何人。乃敢罗织显斥至此。而 殿下置之不问。若俱收并蓄然。是是非非。果如是乎。贤贤恶恶。果如是乎。此臣之所未解也。臣窃见李贵等上年十月。以体察使李德馨召募官。行过居昌。文移陜川。条列仁弘罪目。以一道中士子之停举。守令之黜陟。狱讼流杀之处决。皆出于仁弘之手。又以拥兵七年。营私纵恣等语。令本郡守李馪推问牒报。其惹起衅端。网打士林之计。惨矣。凡有血气。莫不愤惋。而旋念贵亦妄人也已。不足与较。及仁弘承命赴阙。曾未浃辰。贵又上疏。敢仍前语。益肆阴凶。其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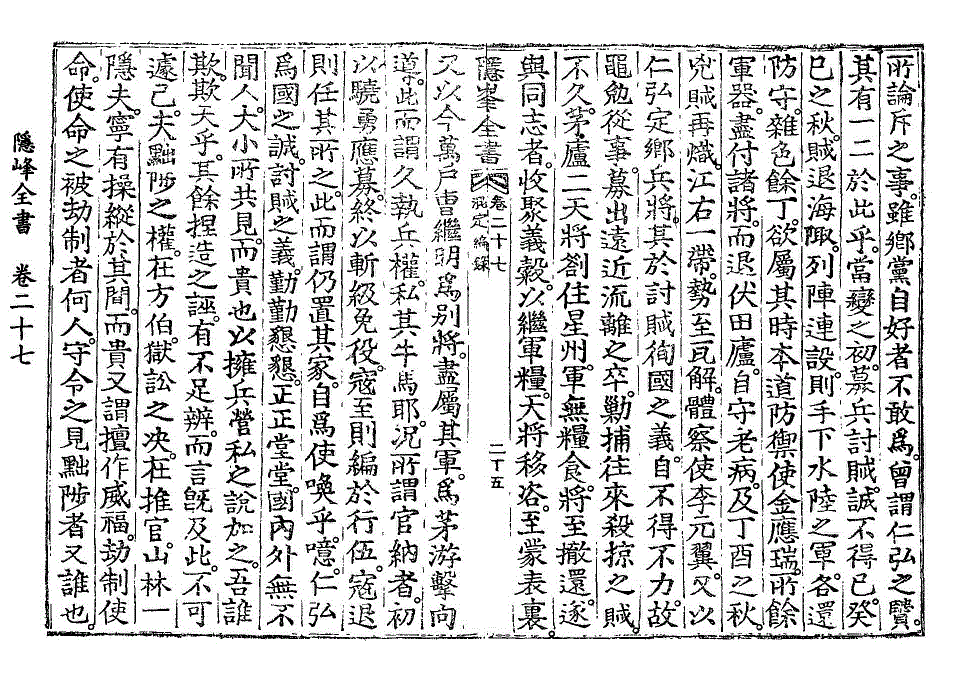 所论斥之事。虽乡党自好者不敢为。曾谓仁弘之贤其有一二于此乎。当变之初。募兵讨贼。诚不得已。癸巳之秋。贼退海陬。列阵连设。则手下水陆之军。各还防守。杂色馀丁。欲属其时本道防御使金应瑞。所馀军器。尽付诸将。而退伏田庐。自守老病。及丁酉之秋。凶贼再炽。江右一带。势至瓦解。体察使李元翼。又以仁弘定乡兵将。其于讨贼徇国之义。自不得不力。故黾勉从事。募出远近流离之卒。剿捕往来杀掠之贼。不久。茅,庐二天将劄住星州。军无粮食。将至撤还。遂与同志者。收聚义谷。以继军粮。天将移咨。至蒙表里。又以今万户曹继明为别将。尽属其军。为茅游击向导。此而谓久执兵权。私其牛马耶。况所谓官纳者。初以骁勇应募。终以斩级免役。寇至则编于行伍。寇退则任其所之。此而谓仍置其家。自为使唤乎。噫。仁弘为国之诚。讨贼之义。勤勤恳恳。正正堂堂。国内外无不闻人。大小所共见。而贵也以拥兵营私之说加之。吾谁欺。欺天乎。其馀捏造之诬。有不足辨。而言既及此。不可遽已。夫黜陟之权。在方伯。狱讼之决。在推官。山林一隐夫。宁有操纵于其间。而贵又谓擅作威福。劫制使命。使命之被劫制者何人。守令之见黜陟者又谁也。
所论斥之事。虽乡党自好者不敢为。曾谓仁弘之贤其有一二于此乎。当变之初。募兵讨贼。诚不得已。癸巳之秋。贼退海陬。列阵连设。则手下水陆之军。各还防守。杂色馀丁。欲属其时本道防御使金应瑞。所馀军器。尽付诸将。而退伏田庐。自守老病。及丁酉之秋。凶贼再炽。江右一带。势至瓦解。体察使李元翼。又以仁弘定乡兵将。其于讨贼徇国之义。自不得不力。故黾勉从事。募出远近流离之卒。剿捕往来杀掠之贼。不久。茅,庐二天将劄住星州。军无粮食。将至撤还。遂与同志者。收聚义谷。以继军粮。天将移咨。至蒙表里。又以今万户曹继明为别将。尽属其军。为茅游击向导。此而谓久执兵权。私其牛马耶。况所谓官纳者。初以骁勇应募。终以斩级免役。寇至则编于行伍。寇退则任其所之。此而谓仍置其家。自为使唤乎。噫。仁弘为国之诚。讨贼之义。勤勤恳恳。正正堂堂。国内外无不闻人。大小所共见。而贵也以拥兵营私之说加之。吾谁欺。欺天乎。其馀捏造之诬。有不足辨。而言既及此。不可遽已。夫黜陟之权。在方伯。狱讼之决。在推官。山林一隐夫。宁有操纵于其间。而贵又谓擅作威福。劫制使命。使命之被劫制者何人。守令之见黜陟者又谁也。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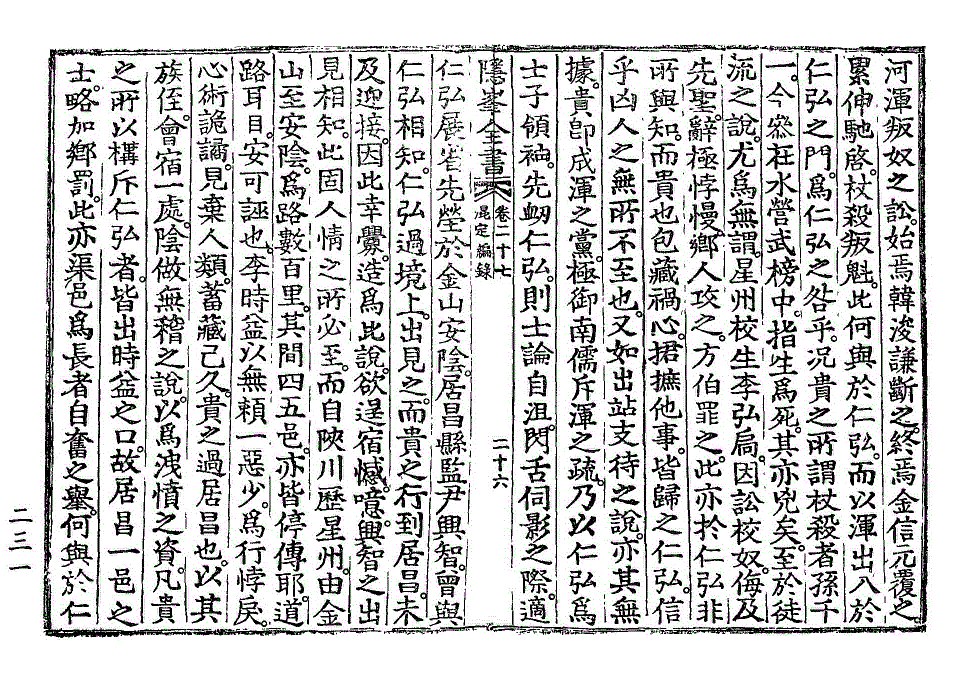 河浑叛奴之讼。始焉韩浚谦断之。终焉金信元覆之。累伸驰启。杖杀叛魁。此何与于仁弘。而以浑出入于仁弘之门。为仁弘之咎乎。况贵之所谓杖杀者孙千一。今参在水营武榜中。指生为死。其亦凶矣。至于徒流之说。尤为无谓。星州校生李弘扃。因讼校奴。侮及先圣。辞极悖慢。乡人攻之。方伯罪之。此亦于仁弘非所与知。而贵也包藏祸心。捃摭他事。皆归之仁弘。信乎凶人之无所不至也。又如出站支待之说。亦其无据。贵即成浑之党。极御南儒斥浑之疏。乃以仁弘为士子领袖。先衄仁弘。则士论自沮。闪舌伺影之际。适仁弘展省先茔于金山安阴。居昌县监尹兴智。曾与仁弘相知。仁弘过境上。出见之。而贵之行到居昌。未及迎接。因此幸衅。造为此说。欲逞宿憾。噫。兴智之出见相知。此固人情之所必至。而自陜川历星州。由金山至安阴。为路数百里。其间四五邑。亦皆停传耶。道路耳目。安可诬也。李时益以无赖一恶少。为行悖戾。心术诡谲。见弃人类。蓄藏已久。贵之过居昌也。以其族侄。会宿一处。阴做无稽之说。以为泄愤之资。凡贵之所以构斥仁弘者。皆出时益之口。故居昌一邑之士。略加乡罚。此亦渠邑为长者自奋之举。何与于仁
河浑叛奴之讼。始焉韩浚谦断之。终焉金信元覆之。累伸驰启。杖杀叛魁。此何与于仁弘。而以浑出入于仁弘之门。为仁弘之咎乎。况贵之所谓杖杀者孙千一。今参在水营武榜中。指生为死。其亦凶矣。至于徒流之说。尤为无谓。星州校生李弘扃。因讼校奴。侮及先圣。辞极悖慢。乡人攻之。方伯罪之。此亦于仁弘非所与知。而贵也包藏祸心。捃摭他事。皆归之仁弘。信乎凶人之无所不至也。又如出站支待之说。亦其无据。贵即成浑之党。极御南儒斥浑之疏。乃以仁弘为士子领袖。先衄仁弘。则士论自沮。闪舌伺影之际。适仁弘展省先茔于金山安阴。居昌县监尹兴智。曾与仁弘相知。仁弘过境上。出见之。而贵之行到居昌。未及迎接。因此幸衅。造为此说。欲逞宿憾。噫。兴智之出见相知。此固人情之所必至。而自陜川历星州。由金山至安阴。为路数百里。其间四五邑。亦皆停传耶。道路耳目。安可诬也。李时益以无赖一恶少。为行悖戾。心术诡谲。见弃人类。蓄藏已久。贵之过居昌也。以其族侄。会宿一处。阴做无稽之说。以为泄愤之资。凡贵之所以构斥仁弘者。皆出时益之口。故居昌一邑之士。略加乡罚。此亦渠邑为长者自奋之举。何与于仁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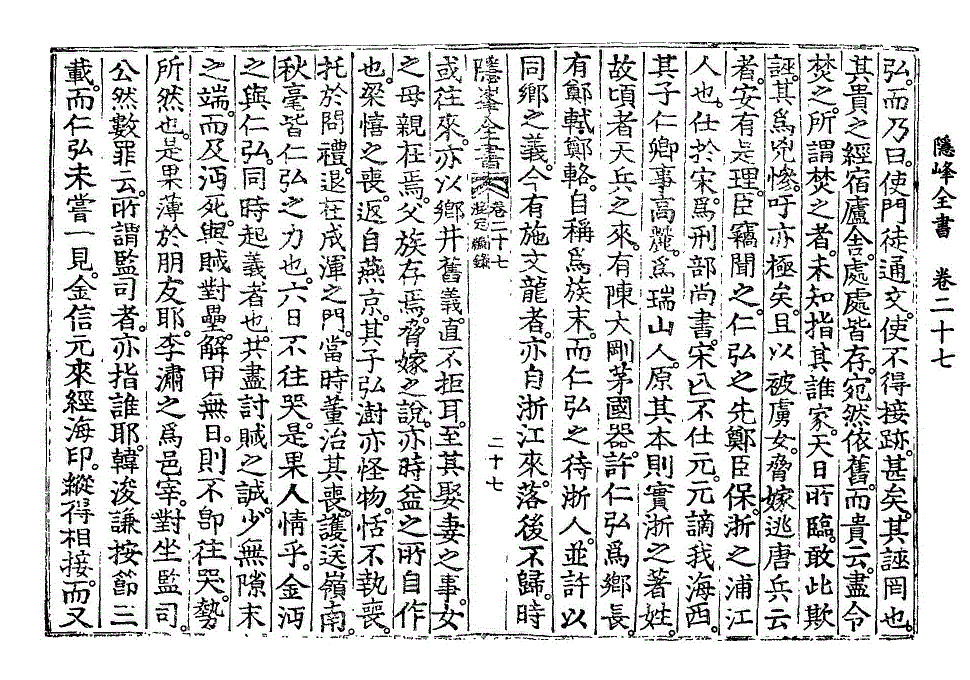 弘。而乃曰。使门徒通文。使不得接迹。甚矣。其诬罔也。其贵之经宿庐舍。处处皆存。宛然依旧。而贵云。尽令焚之。所谓焚之者。未知指其谁家。天日所临。敢此欺诬。其为凶惨。吁亦极矣。且以被虏女。胁嫁逃唐兵云者。安有是理。臣窃闻之。仁弘之先郑臣保。浙之浦江人也。仕于宋。为刑部尚书。宋亡不仕元。元谪我海西。其子仁卿事高丽。为瑞山人。原其本则实浙之著姓。故顷者天兵之来。有陈大刚,茅国器。许仁弘为乡长。有郑轼,郑辂。自称为族末。而仁弘之待浙人。并许以同乡之义。今有施文龙者。亦自浙江来。落后不归。时或往来。亦以乡井旧义。直不拒耳。至其娶妻之事。女之母亲在焉。父族存焉。胁嫁之说。亦时益之所自作也。梁憘之丧。返自燕京。其子弘澍亦怪物。恬不执丧。托于问礼。退在成浑之门。当时董治其丧。护送岭南。秋毫皆仁弘之力也。六日不往哭。是果人情乎。金沔之与仁弘。同时起义者也。共尽讨贼之诚。少无隙末之端。而及沔死。与贼对垒。解甲无日。则不即往哭。势所然也。是果薄于朋友耶。李潚之为邑宰。对坐监司。公然数罪云。所谓监司者。亦指谁耶。韩浚谦按节三载。而仁弘未尝一见。金信元来经海印。纵得相接。而又
弘。而乃曰。使门徒通文。使不得接迹。甚矣。其诬罔也。其贵之经宿庐舍。处处皆存。宛然依旧。而贵云。尽令焚之。所谓焚之者。未知指其谁家。天日所临。敢此欺诬。其为凶惨。吁亦极矣。且以被虏女。胁嫁逃唐兵云者。安有是理。臣窃闻之。仁弘之先郑臣保。浙之浦江人也。仕于宋。为刑部尚书。宋亡不仕元。元谪我海西。其子仁卿事高丽。为瑞山人。原其本则实浙之著姓。故顷者天兵之来。有陈大刚,茅国器。许仁弘为乡长。有郑轼,郑辂。自称为族末。而仁弘之待浙人。并许以同乡之义。今有施文龙者。亦自浙江来。落后不归。时或往来。亦以乡井旧义。直不拒耳。至其娶妻之事。女之母亲在焉。父族存焉。胁嫁之说。亦时益之所自作也。梁憘之丧。返自燕京。其子弘澍亦怪物。恬不执丧。托于问礼。退在成浑之门。当时董治其丧。护送岭南。秋毫皆仁弘之力也。六日不往哭。是果人情乎。金沔之与仁弘。同时起义者也。共尽讨贼之诚。少无隙末之端。而及沔死。与贼对垒。解甲无日。则不即往哭。势所然也。是果薄于朋友耶。李潚之为邑宰。对坐监司。公然数罪云。所谓监司者。亦指谁耶。韩浚谦按节三载。而仁弘未尝一见。金信元来经海印。纵得相接。而又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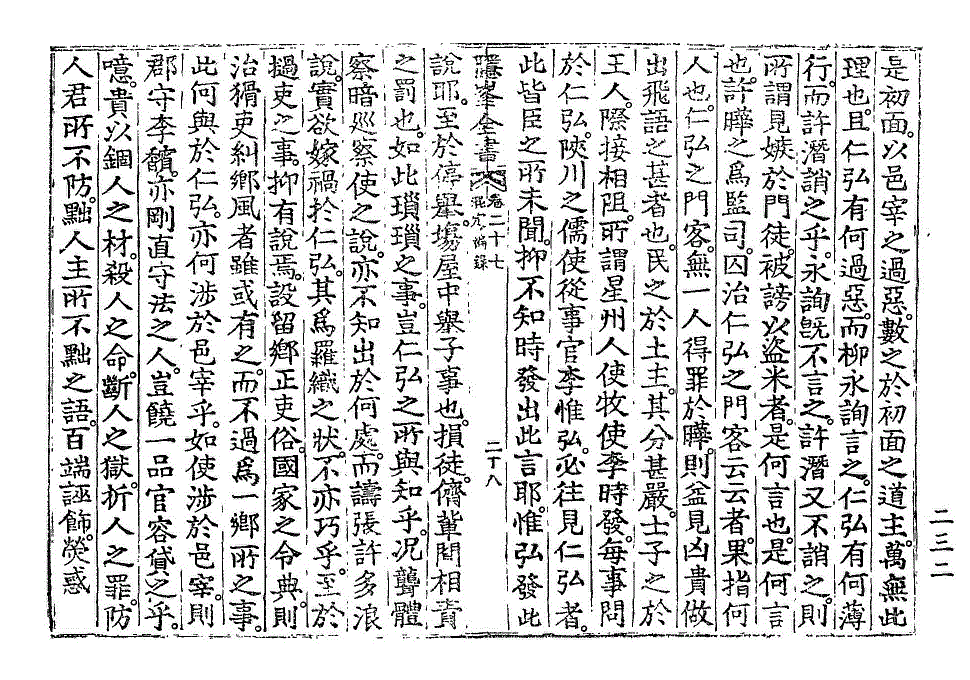 是初面。以邑宰之过恶。数之于初面之道主。万无此理也。且仁弘有何过恶。而柳永询言之。仁弘有何薄行。而许潜诮之乎。永询既不言之。许潜又不诮之。则所谓见嫉于门徒。被谤以盗米者。是何言也。是何言也。许晔之为监司。囚治仁弘之门客云云者。果指何人也。仁弘之门客。无一人得罪于晔。则益见凶贵做出飞语之甚者也。民之于土主。其分甚严。士子之于王人。际接相阻。所谓星州人使牧使李时发。每事问于仁弘。陜川之儒使从事官李惟弘。必往见仁弘者。此皆臣之所未闻。抑不知时发出此言耶。惟弘发此说耶。至于停举。场屋中举子事也。损徒。侪辈间相责之罚也。如此琐琐之事。岂仁弘之所与知乎。况聋体察暗巡察使之说。亦不知出于何处。而诪张许多浪说。实欲嫁祸于仁弘。其为罗织之状。不亦巧乎。至于挝吏之事。抑有说焉。设留乡正吏俗。国家之令典。则治猾吏纠乡风者虽或有之。而不过为一乡所之事。此何与于仁弘。亦何涉于邑宰乎。如使涉于邑宰。则郡守李馪。亦刚直守法之人。岂饶一品官容贷之乎。噫。贵以锢人之材。杀人之命。断人之狱。折人之罪。防人君所不防。黜人主所不黜之语。百端诬饰。荧惑
是初面。以邑宰之过恶。数之于初面之道主。万无此理也。且仁弘有何过恶。而柳永询言之。仁弘有何薄行。而许潜诮之乎。永询既不言之。许潜又不诮之。则所谓见嫉于门徒。被谤以盗米者。是何言也。是何言也。许晔之为监司。囚治仁弘之门客云云者。果指何人也。仁弘之门客。无一人得罪于晔。则益见凶贵做出飞语之甚者也。民之于土主。其分甚严。士子之于王人。际接相阻。所谓星州人使牧使李时发。每事问于仁弘。陜川之儒使从事官李惟弘。必往见仁弘者。此皆臣之所未闻。抑不知时发出此言耶。惟弘发此说耶。至于停举。场屋中举子事也。损徒。侪辈间相责之罚也。如此琐琐之事。岂仁弘之所与知乎。况聋体察暗巡察使之说。亦不知出于何处。而诪张许多浪说。实欲嫁祸于仁弘。其为罗织之状。不亦巧乎。至于挝吏之事。抑有说焉。设留乡正吏俗。国家之令典。则治猾吏纠乡风者虽或有之。而不过为一乡所之事。此何与于仁弘。亦何涉于邑宰乎。如使涉于邑宰。则郡守李馪。亦刚直守法之人。岂饶一品官容贷之乎。噫。贵以锢人之材。杀人之命。断人之狱。折人之罪。防人君所不防。黜人主所不黜之语。百端诬饰。荧惑 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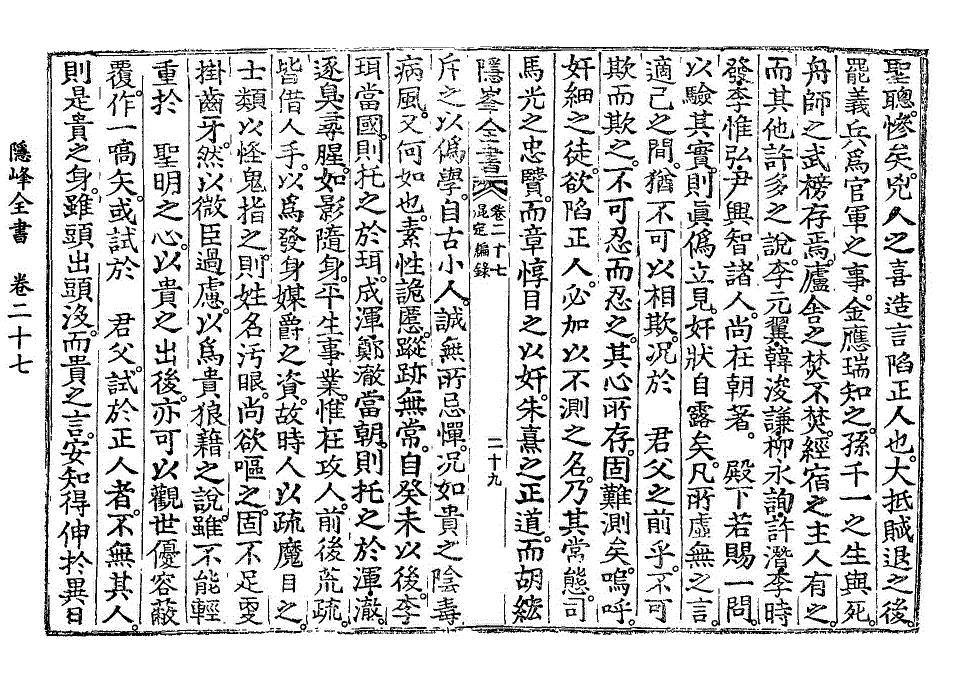 圣聪。惨矣。凶人之喜造言陷正人也。大抵贼退之后。罢义兵为官军之事。金应瑞知之。孙千一之生与死。舟师之武榜存焉。庐舍之焚不焚。经宿之主人有之。而其他许多之说。李元翼,韩浚谦,柳永询,许潜,李时发,李惟弘,尹兴智诸人。尚在朝著。 殿下若赐一问。以验其实。则真伪立见。奸状自露矣。凡所虚无之言。适己之间。犹不可以相欺。况于 君父之前乎。不可欺而欺之。不可忍而忍之。其心所存。固难测矣。呜呼。奸细之徒。欲陷正人。必加以不测之名。乃其常态。司马光之忠贤。而章惇目之以奸。朱熹之正道。而胡纮斥之以伪学。自古小人。诚无所忌惮。况如贵之阴毒病风。又何如也。素性诡慝。踪迹无常。自癸未以后。李珥当国。则托之于珥。成浑,郑澈当朝。则托之于浑,澈。逐臭寻腥。如影随身。平生事业。惟在攻人。前后荒疏。皆借人手。以为发身媒爵之资。故时人以疏魔目之。士类以怪鬼指之。则姓名污眼。尚欲呕之。固不足更挂齿牙。然以微臣过虑。以为贵狼藉之说。虽不能轻重于 圣明之心。以贵之出后。亦可以观世优容蔽覆。作一嗃矢。或试于 君父。试于正人者。不无其人。则是贵之身。虽头出头没。而贵之言。安知得伸于异日
圣聪。惨矣。凶人之喜造言陷正人也。大抵贼退之后。罢义兵为官军之事。金应瑞知之。孙千一之生与死。舟师之武榜存焉。庐舍之焚不焚。经宿之主人有之。而其他许多之说。李元翼,韩浚谦,柳永询,许潜,李时发,李惟弘,尹兴智诸人。尚在朝著。 殿下若赐一问。以验其实。则真伪立见。奸状自露矣。凡所虚无之言。适己之间。犹不可以相欺。况于 君父之前乎。不可欺而欺之。不可忍而忍之。其心所存。固难测矣。呜呼。奸细之徒。欲陷正人。必加以不测之名。乃其常态。司马光之忠贤。而章惇目之以奸。朱熹之正道。而胡纮斥之以伪学。自古小人。诚无所忌惮。况如贵之阴毒病风。又何如也。素性诡慝。踪迹无常。自癸未以后。李珥当国。则托之于珥。成浑,郑澈当朝。则托之于浑,澈。逐臭寻腥。如影随身。平生事业。惟在攻人。前后荒疏。皆借人手。以为发身媒爵之资。故时人以疏魔目之。士类以怪鬼指之。则姓名污眼。尚欲呕之。固不足更挂齿牙。然以微臣过虑。以为贵狼藉之说。虽不能轻重于 圣明之心。以贵之出后。亦可以观世优容蔽覆。作一嗃矢。或试于 君父。试于正人者。不无其人。则是贵之身。虽头出头没。而贵之言。安知得伸于异日隐峰全书卷二十七 第 2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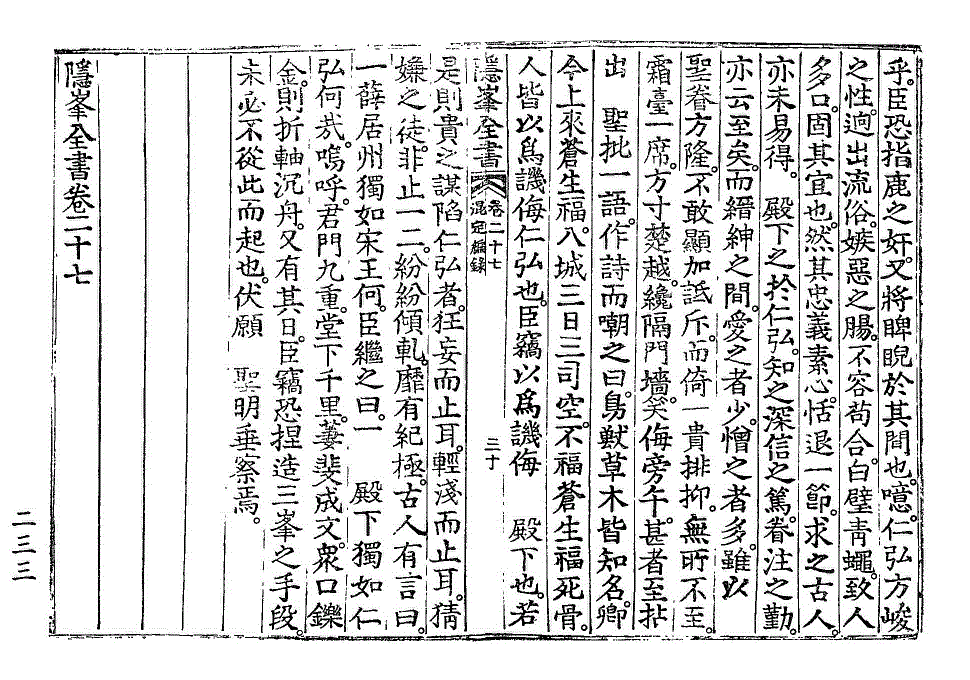 乎。臣恐指鹿之奸。又将睥睨于其间也。噫。仁弘方峻之性。迥出流俗。嫉恶之肠。不容苟合。白璧青蝇。致人多口。固其宜也。然其忠义素心。恬退一节。求之古人。亦未易得。 殿下之于仁弘。知之深信之笃。眷注之勤。亦云至矣。而缙绅之间。爱之者少。憎之者多。虽以 圣眷方隆。不敢显加诋斥。而倚一贵排抑。无所不至。霜台一席。方寸楚越。才隔门墙。笑侮旁午。甚者至拈出 圣批一语。作诗而嘲之曰。鸟兽草木皆知名。卿今上来苍生福。入城三日三司空。不福苍生福死骨。人皆以为讥侮仁弘也。臣窃以为讥侮 殿下也。若是则贵之谋陷仁弘者。狂妄而止耳。轻浅而止耳。猜嫌之徒。非止一二。纷纷倾轧。靡有纪极。古人有言曰。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臣继之曰。一 殿下独如仁弘何哉。呜呼。君门九重。堂下千里。萋斐成文。众口铄金。则折轴沈舟。又有其日。臣窃恐捏造三峰之手段。未必不从此而起也。伏愿 圣明垂察焉。
乎。臣恐指鹿之奸。又将睥睨于其间也。噫。仁弘方峻之性。迥出流俗。嫉恶之肠。不容苟合。白璧青蝇。致人多口。固其宜也。然其忠义素心。恬退一节。求之古人。亦未易得。 殿下之于仁弘。知之深信之笃。眷注之勤。亦云至矣。而缙绅之间。爱之者少。憎之者多。虽以 圣眷方隆。不敢显加诋斥。而倚一贵排抑。无所不至。霜台一席。方寸楚越。才隔门墙。笑侮旁午。甚者至拈出 圣批一语。作诗而嘲之曰。鸟兽草木皆知名。卿今上来苍生福。入城三日三司空。不福苍生福死骨。人皆以为讥侮仁弘也。臣窃以为讥侮 殿下也。若是则贵之谋陷仁弘者。狂妄而止耳。轻浅而止耳。猜嫌之徒。非止一二。纷纷倾轧。靡有纪极。古人有言曰。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臣继之曰。一 殿下独如仁弘何哉。呜呼。君门九重。堂下千里。萋斐成文。众口铄金。则折轴沈舟。又有其日。臣窃恐捏造三峰之手段。未必不从此而起也。伏愿 圣明垂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