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隐峰全书卷二十六 第 x 页
隐峰全书卷二十六
混定编录(后集)
混定编录(后集)
隐峰全书卷二十六 第 2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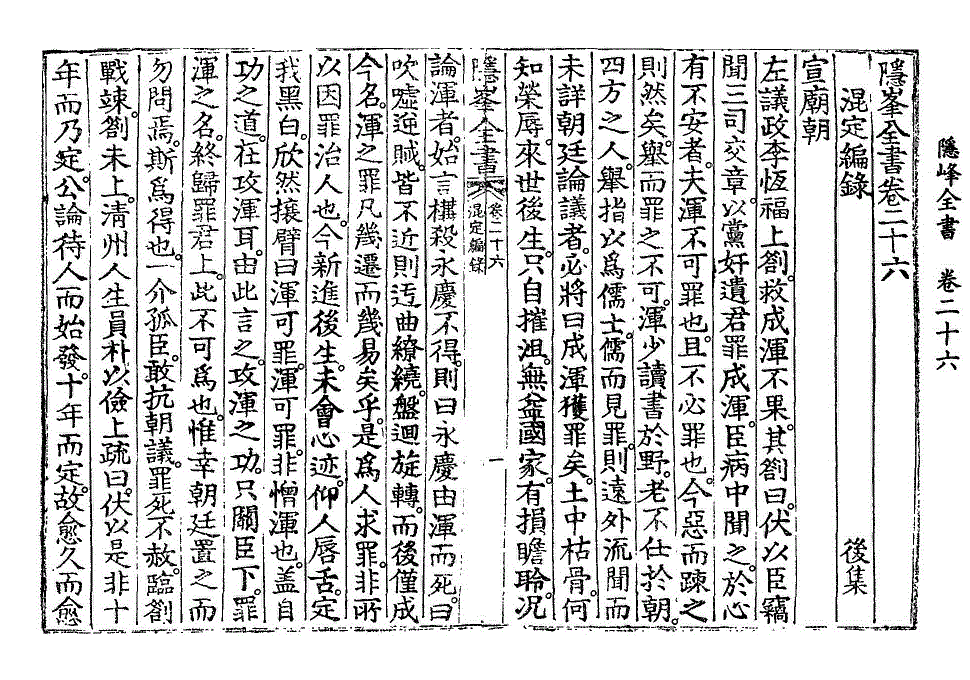 宣庙朝
宣庙朝左议政李恒福上劄。救成浑不果。其劄曰。伏以臣窃闻三司交章。以党奸遗君罪成浑。臣病中闻之。于心有不安者。夫浑不可罪也。且不必罪也。今恶而疏之则然矣。举而罪之不可。浑少读书于野。老不仕于朝。四方之人。举指以为儒士。儒而见罪。则远外流闻而未详朝廷论议者。必将曰成浑获罪矣。土中枯骨。何知荣辱。来世后生。只自摧沮。无益国家。有损瞻聆。况论浑者。始言构杀永庆不得。则曰永庆由浑而死。曰吹嘘逆贼。皆不近则迂曲缭绕。盘回旋转。而后仅成今名。浑之罪凡几迁而几易矣乎。是为人求罪。非所以因罪治人也。今新进后生。未会心迹。仰人唇舌。定我黑白。欣然攘臂曰浑可罪。浑可罪。非憎浑也。盖自功之道。在攻浑耳。由此言之。攻浑之功。只关臣下。罪浑之名。终归罪君上。此不可为也。惟幸朝廷置之而勿问焉。斯为得也。一介孤臣。敢抗朝议。罪死不赦。临劄战竦。劄未上。清州人生员朴以俭上疏曰。伏以是非十年而乃定。公论待人而始发。十年而定。故愈久而愈
隐峰全书卷二十六 第 2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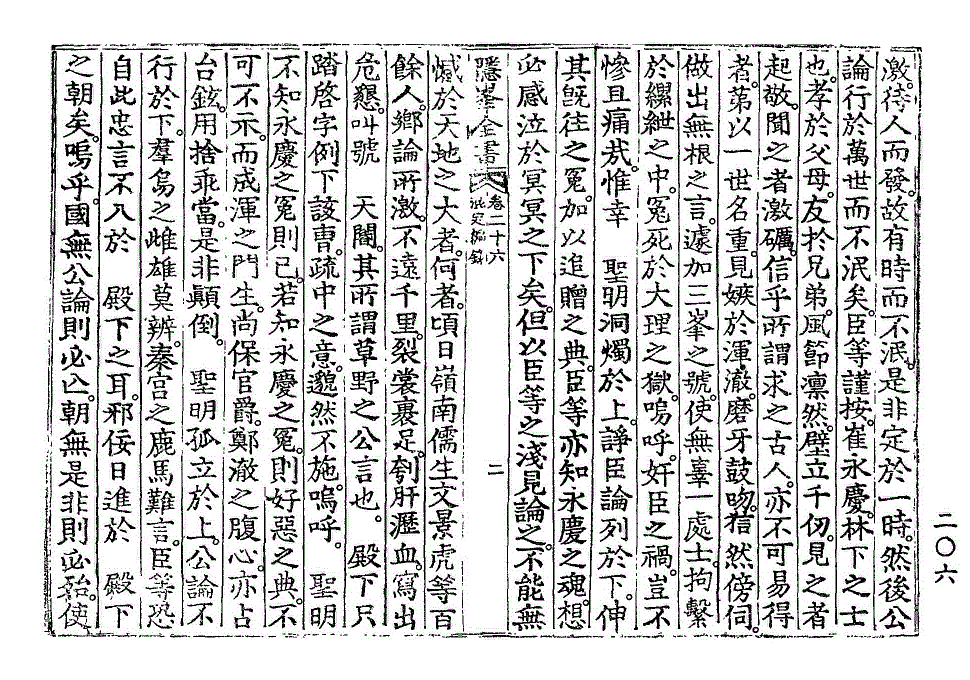 激。待人而发。故有时而不泯。是非定于一时。然后公论行于万世而不泯矣。臣等谨按。崔永庆。林下之士也。孝于父母。友于兄弟。风节凛然。壁立千仞。见之者起敬。闻之者激砺。信乎所谓求之古人。亦不可易得者。第以一世名重。见嫉于浑,澈。磨牙鼓吻。狺然傍伺。做出无根之言。遽加三峰之号。使无辜一处士。拘系于缧绁之中。冤死于大理之狱。呜呼。奸臣之祸。岂不惨且痛哉。惟幸 圣明洞烛于上。诤臣论列于下。伸其既往之冤。加以追赠之典。臣等亦知永庆之魂。想必感泣于冥冥之下矣。但以臣等之浅见论之。不能无憾于天地之大者。何者。顷日岭南儒生文景虎等百馀人。乡论所激。不远千里。裂裳裹足。刳肝沥血。写出危恳。叫号 天阍。其所谓草野之公言也。 殿下只踏启字例下该曹。疏中之意。邈然不施。呜呼。 圣明不知永庆之冤则已。若知永庆之冤。则好恶之典。不可不示。而成浑之门生。尚保官爵。郑澈之腹心。亦占台铉。用舍乖当。是非颠倒。 圣明孤立于上。公论不行于下。群乌之雌雄莫辨。秦宫之鹿马难言。臣等恐自此忠言不入于 殿下之耳。邪佞日进于 殿下之朝矣。呜乎。国无公论则必亡。朝无是非则必殆。使
激。待人而发。故有时而不泯。是非定于一时。然后公论行于万世而不泯矣。臣等谨按。崔永庆。林下之士也。孝于父母。友于兄弟。风节凛然。壁立千仞。见之者起敬。闻之者激砺。信乎所谓求之古人。亦不可易得者。第以一世名重。见嫉于浑,澈。磨牙鼓吻。狺然傍伺。做出无根之言。遽加三峰之号。使无辜一处士。拘系于缧绁之中。冤死于大理之狱。呜呼。奸臣之祸。岂不惨且痛哉。惟幸 圣明洞烛于上。诤臣论列于下。伸其既往之冤。加以追赠之典。臣等亦知永庆之魂。想必感泣于冥冥之下矣。但以臣等之浅见论之。不能无憾于天地之大者。何者。顷日岭南儒生文景虎等百馀人。乡论所激。不远千里。裂裳裹足。刳肝沥血。写出危恳。叫号 天阍。其所谓草野之公言也。 殿下只踏启字例下该曹。疏中之意。邈然不施。呜呼。 圣明不知永庆之冤则已。若知永庆之冤。则好恶之典。不可不示。而成浑之门生。尚保官爵。郑澈之腹心。亦占台铉。用舍乖当。是非颠倒。 圣明孤立于上。公论不行于下。群乌之雌雄莫辨。秦宫之鹿马难言。臣等恐自此忠言不入于 殿下之耳。邪佞日进于 殿下之朝矣。呜乎。国无公论则必亡。朝无是非则必殆。使隐峰全书卷二十六 第 2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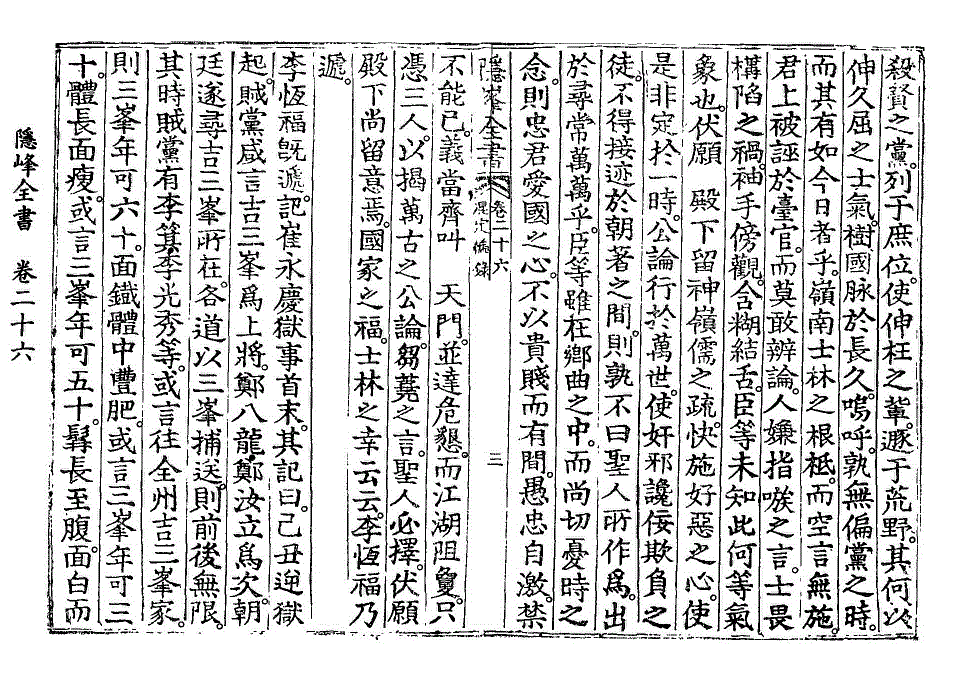 杀贤之党。列于庶位。使伸枉之辈。遁于荒野。其何以伸久屈之士气。树国脉于长久。呜呼。孰无偏党之时。而其有如今日者乎。岭南士林之根柢。而空言无施。君上被诬于台官。而莫敢辨论。人嫌指嗾之言。士畏构陷之祸。袖手傍观。含糊结舌。臣等未知此何等气象也。伏愿 殿下留神岭儒之疏。快施好恶之心。使是非定于一时。公论行于万世。使奸邪谗佞欺负之徒。不得接迹于朝著之间。则孰不曰圣人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乎。臣等虽在乡曲之中。而尚切忧时之念。则忠君爱国之心。不以贵贱而有间。愚忠自激。禁不能已。义当齐叫 天门。并达危恳。而江湖阻夐。只凭三人。以揭万古之公论。刍荛之言。圣人必择。伏愿殿下尚留意焉。国家之福。士林之幸云云。李恒福乃递。
杀贤之党。列于庶位。使伸枉之辈。遁于荒野。其何以伸久屈之士气。树国脉于长久。呜呼。孰无偏党之时。而其有如今日者乎。岭南士林之根柢。而空言无施。君上被诬于台官。而莫敢辨论。人嫌指嗾之言。士畏构陷之祸。袖手傍观。含糊结舌。臣等未知此何等气象也。伏愿 殿下留神岭儒之疏。快施好恶之心。使是非定于一时。公论行于万世。使奸邪谗佞欺负之徒。不得接迹于朝著之间。则孰不曰圣人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乎。臣等虽在乡曲之中。而尚切忧时之念。则忠君爱国之心。不以贵贱而有间。愚忠自激。禁不能已。义当齐叫 天门。并达危恳。而江湖阻夐。只凭三人。以揭万古之公论。刍荛之言。圣人必择。伏愿殿下尚留意焉。国家之福。士林之幸云云。李恒福乃递。李恒福既递。记崔永庆狱事首末。其记曰。己丑逆狱起。贼党咸言吉三峰为上将。郑八龙,郑汝立为次。朝廷遂寻吉三峰所在。各道以三峰捕送。则前后无限。其时贼党有李箕,李光秀等。或言往全州吉三峰家。则三峰年可六十。面铁体中丰肥。或言三峰年可三十。体长面瘦。或言三峰年可五十。髯长至腹。面白而
隐峰全书卷二十六 第 2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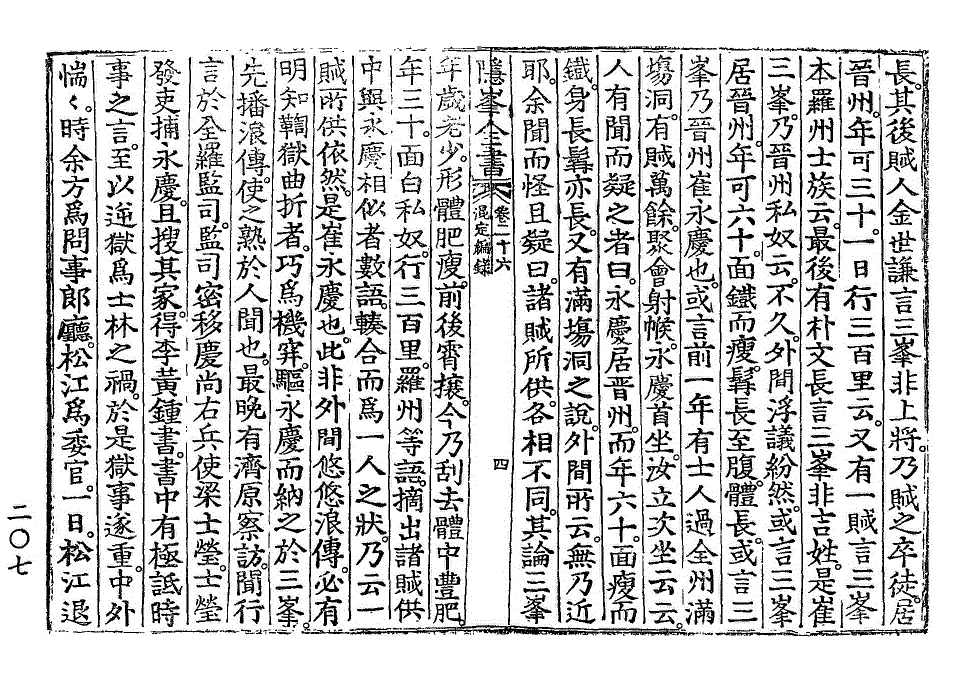 长。其后贼人金世谦言三峰非上将。乃贼之卒徒。居晋州。年可三十。一日行三百里云。又有一贼言三峰本罗州士族云。最后有朴文长言三峰非吉姓。是崔三峰。乃晋州私奴云。不久。外间浮议纷然。或言三峰居晋州。年可六十。面铁而瘦。髯长至腹。体长。或言三峰乃晋州崔永庆也。或言前一年有士人过全州满场洞。有贼万馀。聚会射帿。永庆首坐。汝立次坐云云。人有闻而疑之者曰。永庆居晋州。而年六十。面瘦而铁。身长髯亦长。又有满场洞之说。外间所云。无乃近耶。余闻而怪且疑曰。诸贼所供。各相不同。其论三峰年岁老少。形体肥瘦。前后霄攘。今乃刮去体中丰肥。年三十。面白私奴。行三百里。罗州等语。摘出诸贼供中与永庆相似者数语。辏合而为一人之状。乃云一贼所供依然。是崔永庆也。此非外间悠悠浪传。必有明知鞫狱曲折者。巧为机阱。驱永庆而纳之于三峰。先播浪传。使之熟于人闻也。最晚有济原察访。闻行言于全罗监司。监司密移庆尚右兵使梁士莹。士莹发吏捕永庆。且搜其家。得李黄钟书。书中有极诋时事之言。至以逆狱为士林之祸。于是狱事遂重。中外惴惴。时余方为问事郎厅。松江为委官。一日。松江退
长。其后贼人金世谦言三峰非上将。乃贼之卒徒。居晋州。年可三十。一日行三百里云。又有一贼言三峰本罗州士族云。最后有朴文长言三峰非吉姓。是崔三峰。乃晋州私奴云。不久。外间浮议纷然。或言三峰居晋州。年可六十。面铁而瘦。髯长至腹。体长。或言三峰乃晋州崔永庆也。或言前一年有士人过全州满场洞。有贼万馀。聚会射帿。永庆首坐。汝立次坐云云。人有闻而疑之者曰。永庆居晋州。而年六十。面瘦而铁。身长髯亦长。又有满场洞之说。外间所云。无乃近耶。余闻而怪且疑曰。诸贼所供。各相不同。其论三峰年岁老少。形体肥瘦。前后霄攘。今乃刮去体中丰肥。年三十。面白私奴。行三百里。罗州等语。摘出诸贼供中与永庆相似者数语。辏合而为一人之状。乃云一贼所供依然。是崔永庆也。此非外间悠悠浪传。必有明知鞫狱曲折者。巧为机阱。驱永庆而纳之于三峰。先播浪传。使之熟于人闻也。最晚有济原察访。闻行言于全罗监司。监司密移庆尚右兵使梁士莹。士莹发吏捕永庆。且搜其家。得李黄钟书。书中有极诋时事之言。至以逆狱为士林之祸。于是狱事遂重。中外惴惴。时余方为问事郎厅。松江为委官。一日。松江退隐峰全书卷二十六 第 2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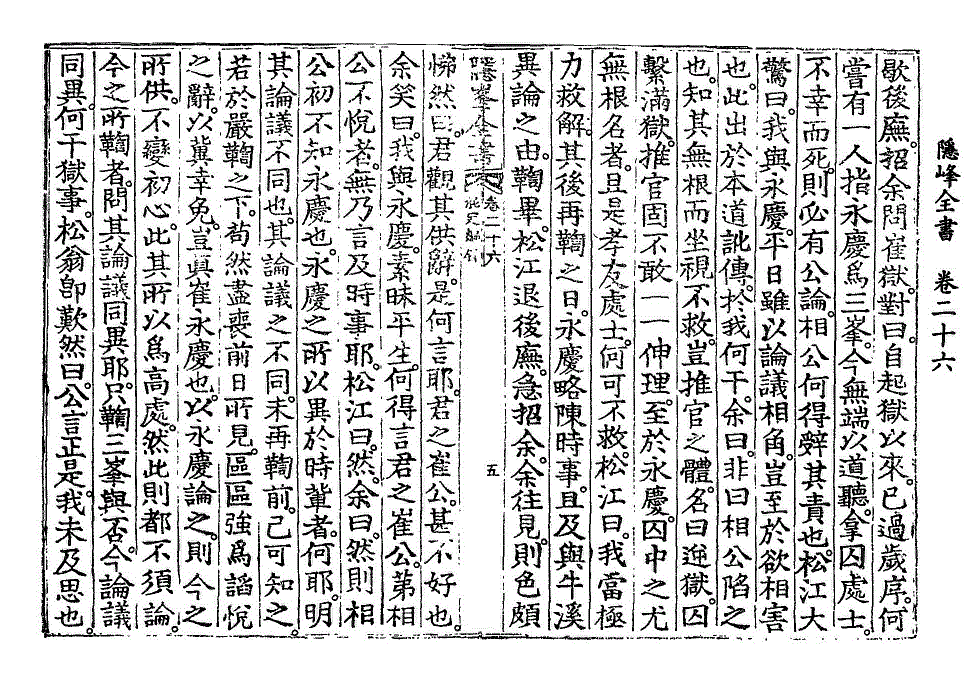 歇后庑。招余问崔狱。对曰。自起狱以来。已过岁序。何尝有一人指永庆为三峰。今无端以道听。拿囚处士。不幸而死。则必有公论。相公何得辞其责也。松江大惊曰。我与永庆。平日虽以论议相角。岂至于欲相害也。此出于本道讹传。于我何干。余曰。非曰相公陷之也。知其无根而坐视不救。岂推官之体。名曰逆狱。囚系满狱。推官固不敢一一伸理。至于永庆。囚中之尤无根名者。且是孝友处士。何可不救。松江曰。我当极力救解。其后再鞫之日。永庆略陈时事。且及与牛溪异论之由。鞫毕。松江退后庑。急招余。余往见。则色颇悌然曰。君观其供辞。是何言耶。君之崔公。甚不好也。余笑曰。我与永庆。素昧平生。何得言君之崔公。第相公不悦者。无乃言及时事耶。松江曰。然。余曰。然则相公初不知永庆也。永庆之所以异于时辈者。何耶。明其论议不同也。其论议之不同。未再鞫前。已可知之。若于严鞫之下。苟然尽丧前日所见。区区强为谄悦之辞。以冀幸免。岂真崔永庆也。以永庆论之。则今之所供。不变初心。此其所以为高处。然此则都不须论。今之所鞫者。问其论议同异耶。只鞫三峰与否。今论议同异。何干狱事。松翁即叹然曰。公言正是。我未及思也。
歇后庑。招余问崔狱。对曰。自起狱以来。已过岁序。何尝有一人指永庆为三峰。今无端以道听。拿囚处士。不幸而死。则必有公论。相公何得辞其责也。松江大惊曰。我与永庆。平日虽以论议相角。岂至于欲相害也。此出于本道讹传。于我何干。余曰。非曰相公陷之也。知其无根而坐视不救。岂推官之体。名曰逆狱。囚系满狱。推官固不敢一一伸理。至于永庆。囚中之尤无根名者。且是孝友处士。何可不救。松江曰。我当极力救解。其后再鞫之日。永庆略陈时事。且及与牛溪异论之由。鞫毕。松江退后庑。急招余。余往见。则色颇悌然曰。君观其供辞。是何言耶。君之崔公。甚不好也。余笑曰。我与永庆。素昧平生。何得言君之崔公。第相公不悦者。无乃言及时事耶。松江曰。然。余曰。然则相公初不知永庆也。永庆之所以异于时辈者。何耶。明其论议不同也。其论议之不同。未再鞫前。已可知之。若于严鞫之下。苟然尽丧前日所见。区区强为谄悦之辞。以冀幸免。岂真崔永庆也。以永庆论之。则今之所供。不变初心。此其所以为高处。然此则都不须论。今之所鞫者。问其论议同异耶。只鞫三峰与否。今论议同异。何干狱事。松翁即叹然曰。公言正是。我未及思也。隐峰全书卷二十六 第 2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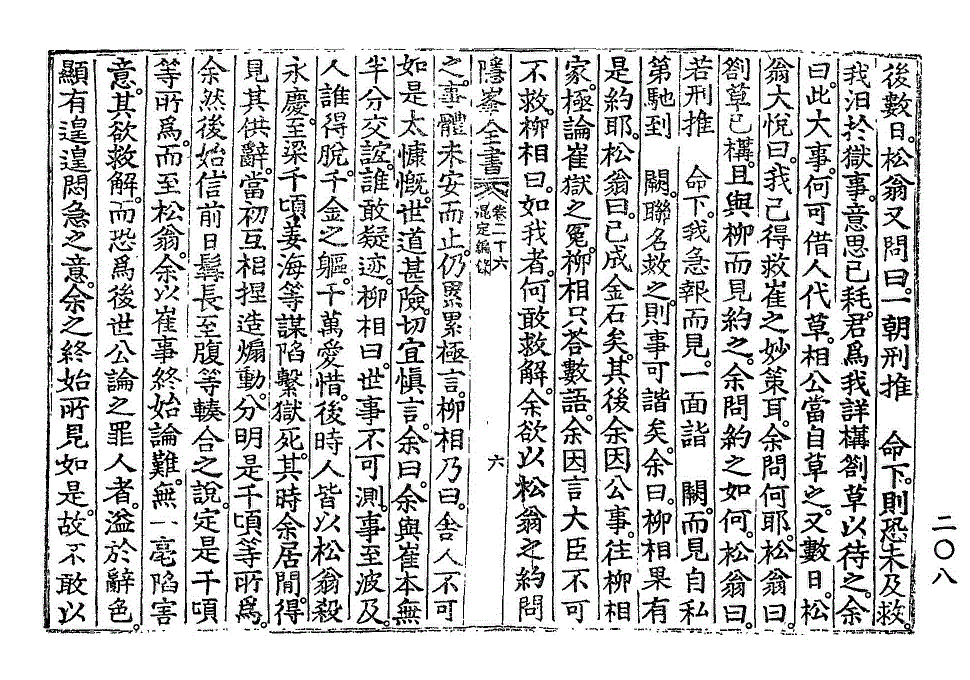 后数日。松翁又问曰。一朝刑推 命下。则恐未及救。我汩于狱事。意思已耗。君为我详构劄草以待之。余曰。此大事。何可借人代草。相公当自草之。又数日。松翁大悦曰。我已得救崔之妙策耳。余问何耶。松翁曰。劄草已构。且与柳而见约之。余问约之如何。松翁曰。若刑推 命下。我急报而见。一面诣 阙。而见自私第驰到 阙。联名救之。则事可谐矣。余曰。柳相果有是约耶。松翁曰。已成金石矣。其后余因公事。往柳相家。极论崔狱之冤。柳相只答数语。余因言大臣不可不救。柳相曰。如我者。何敢救解。余欲以松翁之约问之。事体未安而止。仍累累极言。柳相乃曰。舍人不可如是太慷慨。世道甚险。切宜慎言。余曰。余与崔本无半分交谊。谁敢疑迹。柳相曰。世事不可测。事至波及。人谁得脱。千金之躯。千万爱惜。后时人皆以松翁杀永庆。至梁千顷,姜海等谋陷系狱死。其时余居閒。得见其供辞。当初互相捏造煽动。分明是千顷等所为。余然后始信前日髯长至腹等辏合之说。定是千顷等所为。而至松翁。余以崔事终始论难。无一毫陷害意。其欲救解。而恐为后世公论之罪人者。溢于辞色。显有遑遑闷急之意。余之终始所见如是。故不敢以
后数日。松翁又问曰。一朝刑推 命下。则恐未及救。我汩于狱事。意思已耗。君为我详构劄草以待之。余曰。此大事。何可借人代草。相公当自草之。又数日。松翁大悦曰。我已得救崔之妙策耳。余问何耶。松翁曰。劄草已构。且与柳而见约之。余问约之如何。松翁曰。若刑推 命下。我急报而见。一面诣 阙。而见自私第驰到 阙。联名救之。则事可谐矣。余曰。柳相果有是约耶。松翁曰。已成金石矣。其后余因公事。往柳相家。极论崔狱之冤。柳相只答数语。余因言大臣不可不救。柳相曰。如我者。何敢救解。余欲以松翁之约问之。事体未安而止。仍累累极言。柳相乃曰。舍人不可如是太慷慨。世道甚险。切宜慎言。余曰。余与崔本无半分交谊。谁敢疑迹。柳相曰。世事不可测。事至波及。人谁得脱。千金之躯。千万爱惜。后时人皆以松翁杀永庆。至梁千顷,姜海等谋陷系狱死。其时余居閒。得见其供辞。当初互相捏造煽动。分明是千顷等所为。余然后始信前日髯长至腹等辏合之说。定是千顷等所为。而至松翁。余以崔事终始论难。无一毫陷害意。其欲救解。而恐为后世公论之罪人者。溢于辞色。显有遑遑闷急之意。余之终始所见如是。故不敢以隐峰全书卷二十六 第 2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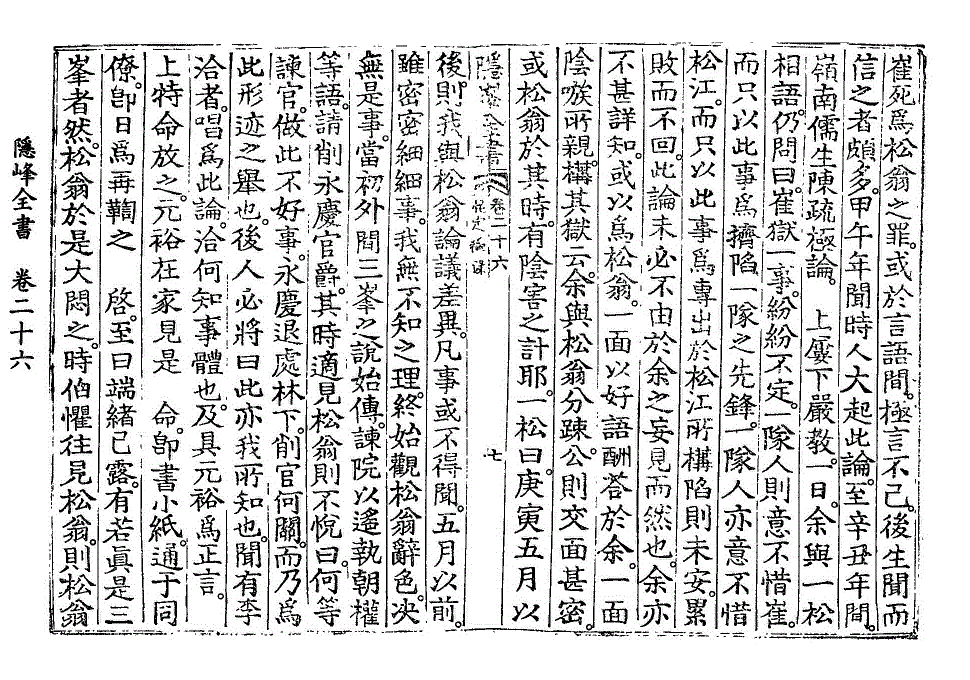 崔死为松翁之罪。或于言语间。极言不已。后生闻而信之者颇多。甲午年闻时人大起此论。至辛丑年间。岭南儒生陈疏极论。 上屡下严教。一日。余与一松相语。仍问曰。崔狱一事。纷纷不定。一队人则意不惜崔。而只以此事为挤陷一队之先锋。一队人亦意不惜松江。而只以此事为专出于松江所构陷则未安。累败而不回。此论未必不由于余之妄见而然也。余亦不甚详知。或以为松翁。一面以好语酬答于余。一面阴嗾所亲。构其狱云。余与松翁分疏。公则交面甚密。或松翁于其时。有阴害之计耶。一松曰。庚寅五月以后。则我与松翁论议差异。凡事或不得闻。五月以前。虽密密细细事。我无不知之理。终始观松翁辞色。决无是事。当初外间三峰之说始传。谏院以遥执朝权等语。请削永庆官爵。其时适见松翁则不悦曰。何等谏官。做此不好事。永庆退处林下。削官何关。而乃为此形迹之举也。后人必将曰此亦我所知也。闻有李洽者。唱为此论。洽何知事体也。及具元裕为正言。 上特命放之。元裕在家见是 命。即书小纸。通于同僚。即日为再鞫之 启。至曰端绪已露。有若真是三峰者然。松翁于是大闷之。时伯惧往见松翁。则松翁
崔死为松翁之罪。或于言语间。极言不已。后生闻而信之者颇多。甲午年闻时人大起此论。至辛丑年间。岭南儒生陈疏极论。 上屡下严教。一日。余与一松相语。仍问曰。崔狱一事。纷纷不定。一队人则意不惜崔。而只以此事为挤陷一队之先锋。一队人亦意不惜松江。而只以此事为专出于松江所构陷则未安。累败而不回。此论未必不由于余之妄见而然也。余亦不甚详知。或以为松翁。一面以好语酬答于余。一面阴嗾所亲。构其狱云。余与松翁分疏。公则交面甚密。或松翁于其时。有阴害之计耶。一松曰。庚寅五月以后。则我与松翁论议差异。凡事或不得闻。五月以前。虽密密细细事。我无不知之理。终始观松翁辞色。决无是事。当初外间三峰之说始传。谏院以遥执朝权等语。请削永庆官爵。其时适见松翁则不悦曰。何等谏官。做此不好事。永庆退处林下。削官何关。而乃为此形迹之举也。后人必将曰此亦我所知也。闻有李洽者。唱为此论。洽何知事体也。及具元裕为正言。 上特命放之。元裕在家见是 命。即书小纸。通于同僚。即日为再鞫之 启。至曰端绪已露。有若真是三峰者然。松翁于是大闷之。时伯惧往见松翁。则松翁隐峰全书卷二十六 第 2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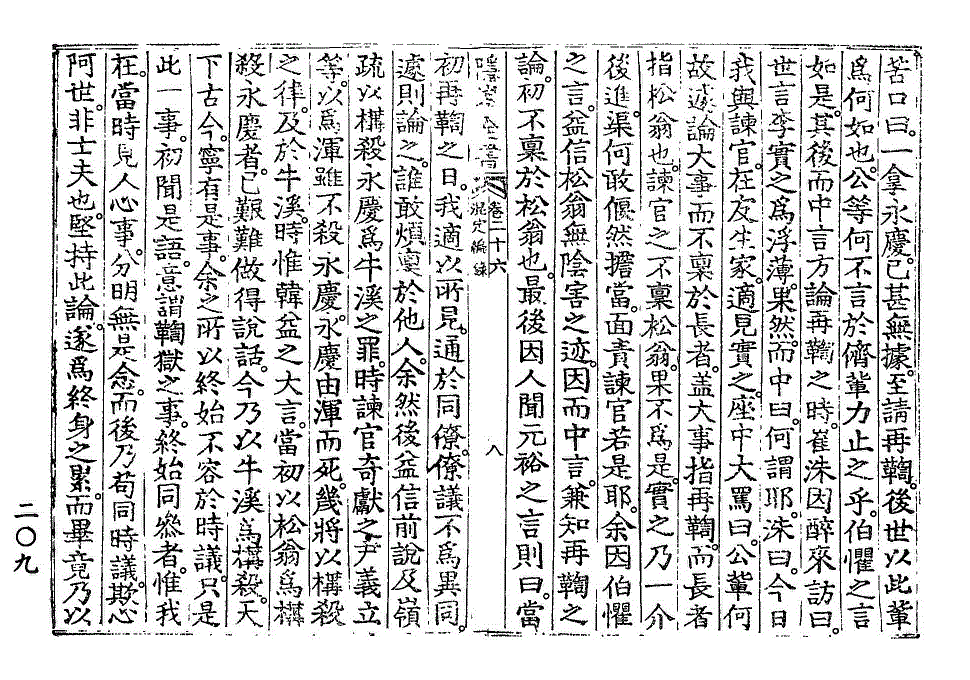 苦口曰。一拿永庆。已甚无据。至请再鞫。后世以此辈为何如也。公等何不言于侪辈力止之乎。伯惧之言如是。其后而中言方论再鞫之时。崔洙因醉来访曰。世言李实之为浮薄。果然。而中曰。何谓耶。洙曰。今日我与谏官。在友生家。适见实之。座中大骂曰。公辈何故遽论大事而不禀于长者。盖大事指再鞫。而长者指松翁也。谏官之不禀松翁。果不为是。实之乃一介后进。渠何敢偃然担当。面责谏官若是耶。余因伯惧之言。益信松翁无阴害之迹。因而中言。兼知再鞫之论。初不禀于松翁也。最后因人闻元裕之言则曰。当初再鞫之日。我适以所见。通于同僚。僚议不为异同。遽则论之。谁敢烦禀于他人。余然后益信前说及岭疏以构杀永庆为牛溪之罪。时谏官奇献之,尹义立等。以为浑虽不杀永庆。永庆由浑而死。几将以构杀之律。及于牛溪。时惟韩益之大言。当初以松翁为构杀永庆者。已艰难做得说话。今乃以牛溪为构杀。天下古今。宁有是事。余之所以终始不容于时议。只是此一事。初闻是语。意谓鞫狱之事。终始同参者。惟我在。当时见人心事。分明无是念。而后乃苟同时议。欺心阿世。非士夫也。坚持此论。遂为终身之累。而毕竟乃以
苦口曰。一拿永庆。已甚无据。至请再鞫。后世以此辈为何如也。公等何不言于侪辈力止之乎。伯惧之言如是。其后而中言方论再鞫之时。崔洙因醉来访曰。世言李实之为浮薄。果然。而中曰。何谓耶。洙曰。今日我与谏官。在友生家。适见实之。座中大骂曰。公辈何故遽论大事而不禀于长者。盖大事指再鞫。而长者指松翁也。谏官之不禀松翁。果不为是。实之乃一介后进。渠何敢偃然担当。面责谏官若是耶。余因伯惧之言。益信松翁无阴害之迹。因而中言。兼知再鞫之论。初不禀于松翁也。最后因人闻元裕之言则曰。当初再鞫之日。我适以所见。通于同僚。僚议不为异同。遽则论之。谁敢烦禀于他人。余然后益信前说及岭疏以构杀永庆为牛溪之罪。时谏官奇献之,尹义立等。以为浑虽不杀永庆。永庆由浑而死。几将以构杀之律。及于牛溪。时惟韩益之大言。当初以松翁为构杀永庆者。已艰难做得说话。今乃以牛溪为构杀。天下古今。宁有是事。余之所以终始不容于时议。只是此一事。初闻是语。意谓鞫狱之事。终始同参者。惟我在。当时见人心事。分明无是念。而后乃苟同时议。欺心阿世。非士夫也。坚持此论。遂为终身之累。而毕竟乃以隐峰全书卷二十六 第 2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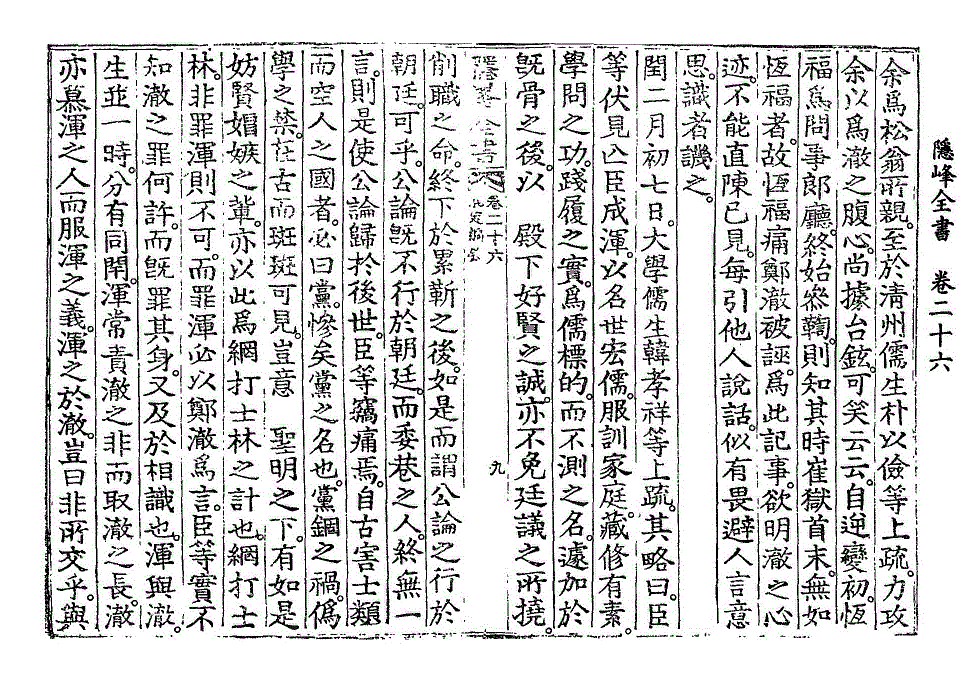 余为松翁所亲。至于清州儒生朴以俭等上疏。力攻余以为澈之腹心。尚据台铉。可笑云云。自逆变初。恒福为问事郎厅。终始参鞫。则知其时崔狱首末。无如恒福者。故恒福痛郑澈被诬。为此记事。欲明澈之心迹。不能直陈己见。每引他人说话。似有畏避人言意思。识者讥之。
余为松翁所亲。至于清州儒生朴以俭等上疏。力攻余以为澈之腹心。尚据台铉。可笑云云。自逆变初。恒福为问事郎厅。终始参鞫。则知其时崔狱首末。无如恒福者。故恒福痛郑澈被诬。为此记事。欲明澈之心迹。不能直陈己见。每引他人说话。似有畏避人言意思。识者讥之。闰二月初七日。大学儒生韩孝祥等上疏。其略曰。臣等伏见亡臣成浑。以名世宏儒。服训家庭。藏修有素。学问之功。践履之实。为儒标的。而不测之名。遽加于既骨之后。以 殿下好贤之诚。亦不免廷议之所挠。削职之命。终下于累靳之后。如是而谓公论之行于朝廷。可乎。公论既不行于朝廷。而委巷之人。终无一言。则是使公论归于后世。臣等窃痛焉。自古害士类而空人之国者。必曰党。惨矣党之名也。党锢之祸。伪学之禁。在古而斑斑可见。岂意 圣明之下。有如是妨贤媢嫉之辈。亦以此为网打士林之计也。纲打士林。非罪浑则不可。而罪浑必以郑澈为言。臣等实不知澈之罪何许。而既罪其身。又及于相识也。浑与澈。生并一时。分有同闬。浑常责澈之非而取澈之长。澈亦慕浑之人而服浑之义。浑之于澈。岂曰非所交乎。与
隐峰全书卷二十六 第 2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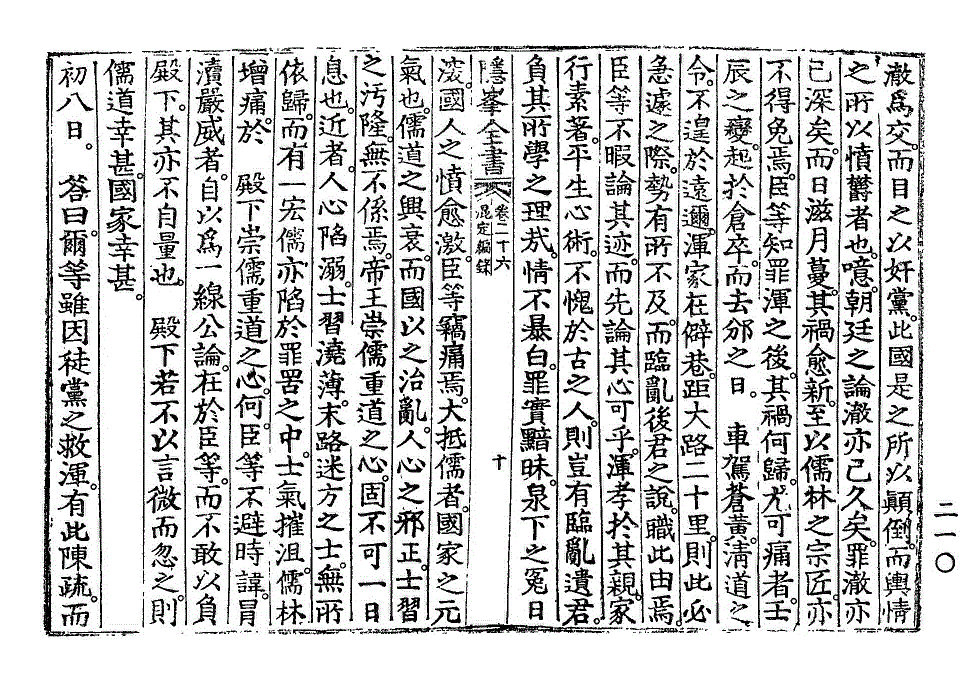 澈为交。而目之以奸党。此国是之所以颠倒。而舆情之所以愤郁者也。噫。朝廷之论澈亦已久矣。罪澈亦已深矣。而日滋月蔓。其祸愈新。至以儒林之宗匠。亦不得免焉。臣等知罪浑之后。其祸何归。尤可痛者。壬辰之变。起于仓卒。而去邠之日。 车驾苍黄。清道之令。不遑于远迩。浑家在僻巷。距大路二十里。则此必急遽之际。势有所不及。而临乱后君之说。职此由焉。臣等不暇论其迹。而先论其心可乎。浑孝于其亲。家行素著。平生心术。不愧于古之人。则岂有临乱遗君。负其所学之理哉。情不暴白。罪实黯昧。泉下之冤日深。国人之愤愈激。臣等窃痛焉。大抵儒者。国家之元气也。儒道之兴衰。而国以之治乱。人心之邪正。士习之污隆。无不系焉。帝王崇儒重道之心。固不可一日息也。近者。人心陷溺。士习浇薄。末路迷方之士。无所依归。而有一宏儒亦陷于罪罟之中。士气摧沮。儒林增痛。于 殿下崇儒重道之心。何。臣等不避时讳。冒渎严威者。自以为一线公论。在于臣等。而不敢以负殿下。其亦不自量也。 殿下若不以言微而忽之。则儒道幸甚。国家幸甚。
澈为交。而目之以奸党。此国是之所以颠倒。而舆情之所以愤郁者也。噫。朝廷之论澈亦已久矣。罪澈亦已深矣。而日滋月蔓。其祸愈新。至以儒林之宗匠。亦不得免焉。臣等知罪浑之后。其祸何归。尤可痛者。壬辰之变。起于仓卒。而去邠之日。 车驾苍黄。清道之令。不遑于远迩。浑家在僻巷。距大路二十里。则此必急遽之际。势有所不及。而临乱后君之说。职此由焉。臣等不暇论其迹。而先论其心可乎。浑孝于其亲。家行素著。平生心术。不愧于古之人。则岂有临乱遗君。负其所学之理哉。情不暴白。罪实黯昧。泉下之冤日深。国人之愤愈激。臣等窃痛焉。大抵儒者。国家之元气也。儒道之兴衰。而国以之治乱。人心之邪正。士习之污隆。无不系焉。帝王崇儒重道之心。固不可一日息也。近者。人心陷溺。士习浇薄。末路迷方之士。无所依归。而有一宏儒亦陷于罪罟之中。士气摧沮。儒林增痛。于 殿下崇儒重道之心。何。臣等不避时讳。冒渎严威者。自以为一线公论。在于臣等。而不敢以负殿下。其亦不自量也。 殿下若不以言微而忽之。则儒道幸甚。国家幸甚。初八日。 答曰。尔等虽因徒党之救浑。有此陈疏。而
隐峰全书卷二十六 第 211H 页
 其交结奸凶之状。则虽尔等。亦不能掩焉。然则尔等之说。不攻而自破。欲盖而弥彰者也。至以浑为宏儒。何其辱哉。儒之名称。固亦非一。设使浑粗习章句。目之以儒。既合奸凶为一体。视君父如弊屣。终乃导君父。乞降雠贼。是乃扬墨之类也。能言距扬墨者。圣人之徒也。今朝廷之讨其罪。皆据其已著之情状。在人耳目。昭不可掩者。正所以定是非于万世。初非钩摘隐慝。加之以情外之律也。大抵儒生之道。但当读书藏修而已。朝廷之是非。非所当预。其知予意。
其交结奸凶之状。则虽尔等。亦不能掩焉。然则尔等之说。不攻而自破。欲盖而弥彰者也。至以浑为宏儒。何其辱哉。儒之名称。固亦非一。设使浑粗习章句。目之以儒。既合奸凶为一体。视君父如弊屣。终乃导君父。乞降雠贼。是乃扬墨之类也。能言距扬墨者。圣人之徒也。今朝廷之讨其罪。皆据其已著之情状。在人耳目。昭不可掩者。正所以定是非于万世。初非钩摘隐慝。加之以情外之律也。大抵儒生之道。但当读书藏修而已。朝廷之是非。非所当预。其知予意。掌令姜签 启曰。顷日。玉堂论劄成浑后君党奸之罪。而臣亦以应教同参矣。今者显被韩孝祥等之诋斥。至曰妨贤媢嫉之辈。网打士林之计。不可腼然仍冒言地。请 命递臣职。 答曰。勿辞。退待物论。
执义李效元,掌令姜弘立等避嫌 启曰。成浑党奸后君之罪。国人之所共知。 殿下之所洞烛。臣等之论劾追削。不过欲定是非恢公论而已。今见生员韩孝祥等疏中为浑营救。极其诪张。至有妨贤媢嫉之辈。亦以此为网打士林之计之语。臣等被人显斥。决难仍冒言地。请 命递臣等之职。 答曰。勿辞。退待物论。
隐峰全书卷二十六 第 2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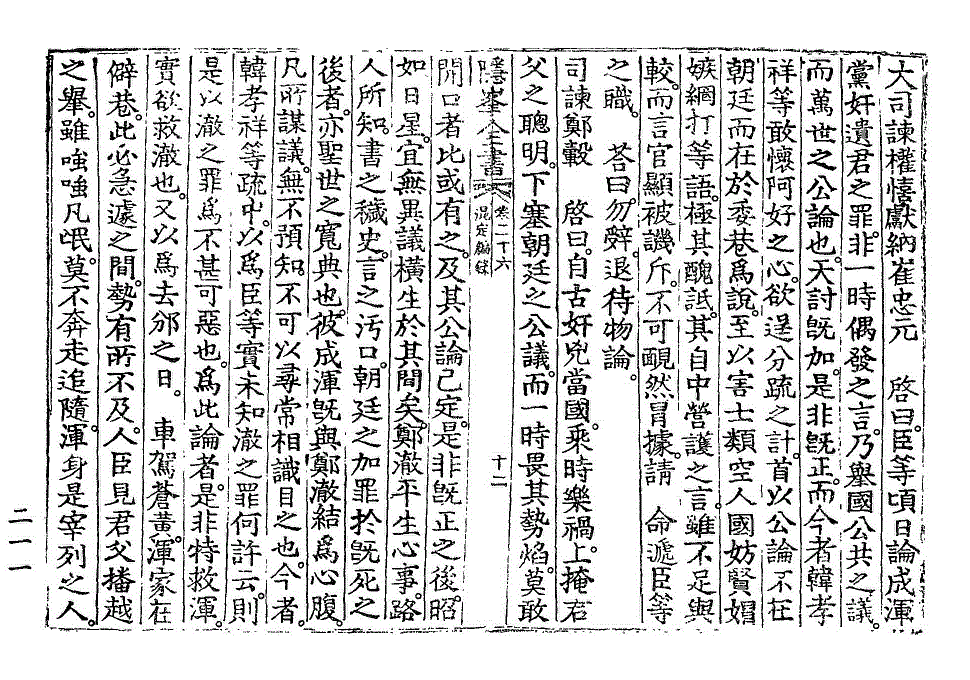 大司谏权憘,献纳崔忠元 启曰。臣等顷日论成浑党奸遗君之罪。非一时偶发之言。乃举国公共之议。而万世之公论也。天讨既加。是非既正。而今者韩孝祥等敢怀阿好之心。欲逞分疏之计。首以公论不在朝廷而在于委巷为说。至以害士类空人国妨贤媢嫉网打等语。极其丑诋。其自中营护之言。虽不足与较。而言官显被讥斥。不可腼然冒据。请 命递臣等之职。 答曰。勿辞。退待物论。
大司谏权憘,献纳崔忠元 启曰。臣等顷日论成浑党奸遗君之罪。非一时偶发之言。乃举国公共之议。而万世之公论也。天讨既加。是非既正。而今者韩孝祥等敢怀阿好之心。欲逞分疏之计。首以公论不在朝廷而在于委巷为说。至以害士类空人国妨贤媢嫉网打等语。极其丑诋。其自中营护之言。虽不足与较。而言官显被讥斥。不可腼然冒据。请 命递臣等之职。 答曰。勿辞。退待物论。司谏郑毂 启曰。自吉奸凶当国。乘时乐祸。上掩君父之聪明。下塞朝廷之公议。而一时畏其势焰。莫敢开口者比或有之。及其公论已定。是非既正之后。昭如日星。宜无异议横生于其间矣。郑澈平生心事。路人所知。书之秽史。言之污口。朝廷之加罪于既死之后者。亦圣世之宽典也。彼成浑既与郑澈结为心腹。凡所谋议。无不预知。不可以寻常相识目之也。今者。韩孝祥等疏中。以为臣等实未知澈之罪何许云。则是以澈之罪为不甚可恶也。为此论者。是非特救浑。实欲救澈也。又以为去邠之日。 车驾苍黄。浑家在僻巷。此必急遽之间。势有所不及。人臣见君父播越之举。虽嗤嗤凡氓。莫不奔走追随。浑身是宰列之人。
隐峰全书卷二十六 第 2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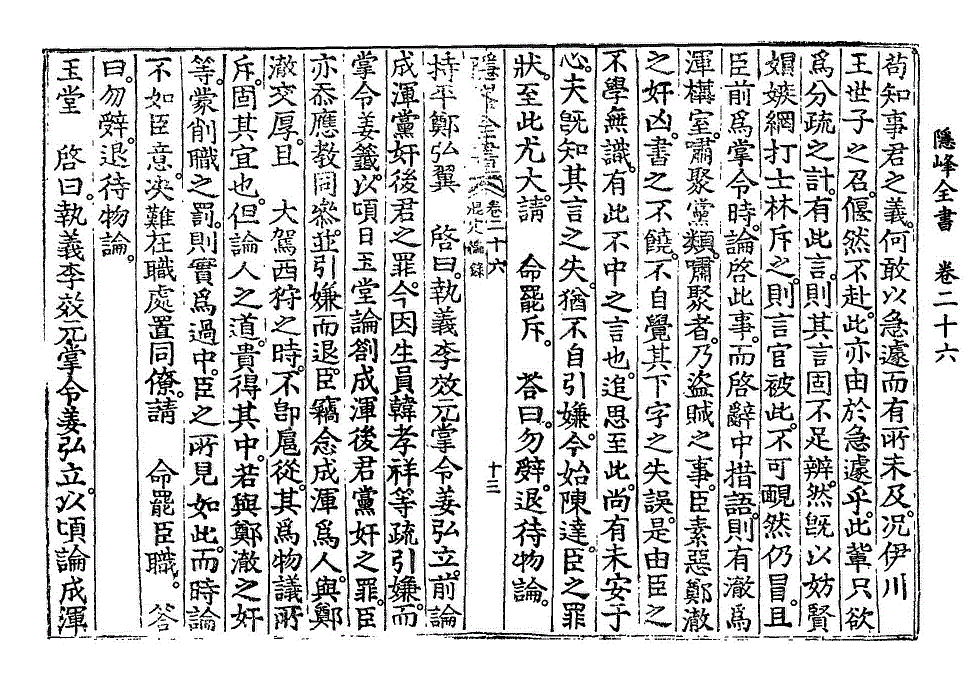 苟知事君之义。何敢以急遽而有所未及。况伊川 王世子之召。偃然不赴。此亦由于急遽乎。此辈只欲为分疏之计。有此言。则其言固不足辨。然既以妨贤媢嫉网打士林斥之。则言官被此。不可腼然仍冒。且臣前为掌令时。论启此事。而启辞中措语。则有澈为浑构室。啸聚党类。啸聚者。乃盗贼之事。臣素恶郑澈之奸凶。书之不饶。不自觉其下字之失误。是由臣之不学无识。有此不中之言也。追思至此。尚有未安于心。夫既知其言之失。犹不自引嫌。今始陈达。臣之罪状。至此尤大。请 命罢斥。 答曰。勿辞。退待物论。
苟知事君之义。何敢以急遽而有所未及。况伊川 王世子之召。偃然不赴。此亦由于急遽乎。此辈只欲为分疏之计。有此言。则其言固不足辨。然既以妨贤媢嫉网打士林斥之。则言官被此。不可腼然仍冒。且臣前为掌令时。论启此事。而启辞中措语。则有澈为浑构室。啸聚党类。啸聚者。乃盗贼之事。臣素恶郑澈之奸凶。书之不饶。不自觉其下字之失误。是由臣之不学无识。有此不中之言也。追思至此。尚有未安于心。夫既知其言之失。犹不自引嫌。今始陈达。臣之罪状。至此尤大。请 命罢斥。 答曰。勿辞。退待物论。持平郑弘翼 启曰。执义李效元,掌令姜弘立。前论成浑党奸后君之罪。今因生员韩孝祥等疏引嫌。而掌令姜签。以顷日玉堂论劄成浑后君党奸之罪。臣亦忝应教同参。并引嫌而退。臣窃念成浑为人。与郑澈交厚。且 大驾西狩之时。不即扈从。其为物议所斥。固其宜也。但论人之道。贵得其中。若与郑澈之奸等。蒙削职之罚。则实为过中。臣之所见如此。而时论不如臣意。决难在职处置同僚。请 命罢臣职。 答曰。勿辞。退待物论。
玉堂 启曰。执义李效元,掌令姜弘立。以顷论成浑
隐峰全书卷二十六 第 2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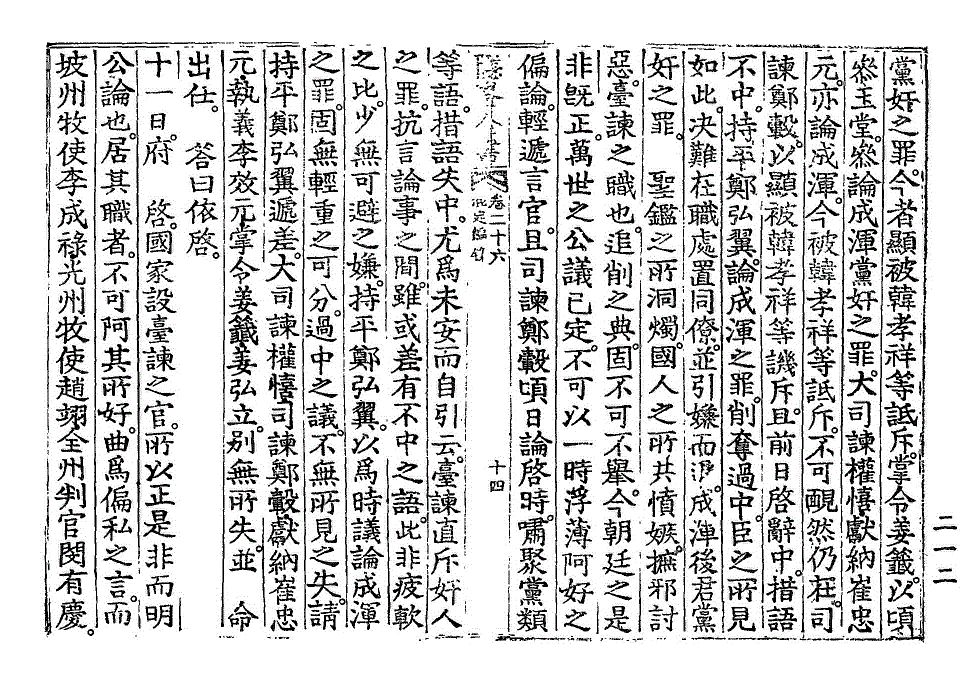 党奸之罪。今者显被韩孝祥等诋斥。掌令姜签。以顷参玉堂。参论成浑党奸之罪。大司谏权憘,献纳崔忠元。亦论成浑。今被韩孝祥等诋斥。不可腼然仍在。司谏郑毂。以显被韩孝祥等讥斥。且前日启辞中。措语不中。持平郑弘翼。论成浑之罪。削夺过中。臣之所见如此。决难在职处置同僚。并引嫌而退。成浑后君党奸之罪。 圣鉴之所洞烛。国人之所共愤嫉。摭邪讨恶。台谏之职也。追削之典。固不可不举。今朝廷之是非既正。万世之公议已定。不可以一时浮薄阿好之偏论。轻递言官。且司谏郑毂顷日论启时。啸聚党类等语。措语失中。尤为未安而自引云。台谏直斥奸人之罪。抗言论事之间。虽或差有不中之语。此非疲软之比。少无可避之嫌。持平郑弘翼。以为时议论成浑之罪。固无轻重之可分。过中之议。不无所见之失。请持平郑弘翼递差。大司谏权憘,司谏郑毂,献纳崔忠元,执义李效元,掌令姜签,姜弘立。别无所失。并 命出仕。 答曰依启。
党奸之罪。今者显被韩孝祥等诋斥。掌令姜签。以顷参玉堂。参论成浑党奸之罪。大司谏权憘,献纳崔忠元。亦论成浑。今被韩孝祥等诋斥。不可腼然仍在。司谏郑毂。以显被韩孝祥等讥斥。且前日启辞中。措语不中。持平郑弘翼。论成浑之罪。削夺过中。臣之所见如此。决难在职处置同僚。并引嫌而退。成浑后君党奸之罪。 圣鉴之所洞烛。国人之所共愤嫉。摭邪讨恶。台谏之职也。追削之典。固不可不举。今朝廷之是非既正。万世之公议已定。不可以一时浮薄阿好之偏论。轻递言官。且司谏郑毂顷日论启时。啸聚党类等语。措语失中。尤为未安而自引云。台谏直斥奸人之罪。抗言论事之间。虽或差有不中之语。此非疲软之比。少无可避之嫌。持平郑弘翼。以为时议论成浑之罪。固无轻重之可分。过中之议。不无所见之失。请持平郑弘翼递差。大司谏权憘,司谏郑毂,献纳崔忠元,执义李效元,掌令姜签,姜弘立。别无所失。并 命出仕。 答曰依启。十一日。府 启。国家设台谏之官。所以正是非而明公论也。居其职者。不可阿其所好。曲为偏私之言。而坡州牧使李成禄,光州牧使赵翊,全州判官闵有庆。
隐峰全书卷二十六 第 2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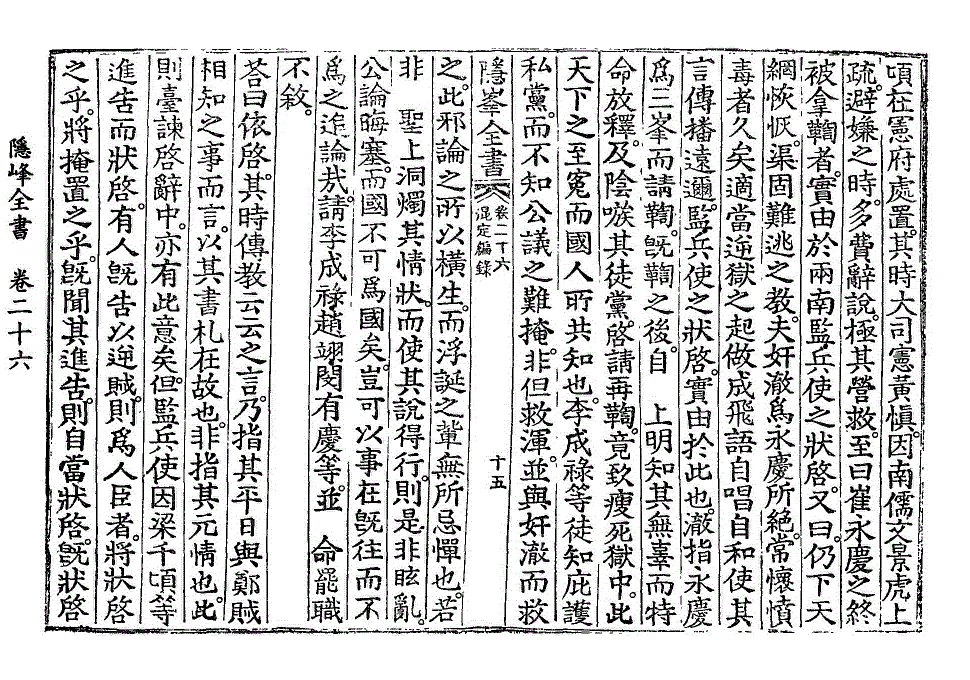 顷在宪府处置。其时大司宪黄慎。因南儒文景虎上疏。避嫌之时。多费辞说。极其营救。至曰崔永庆之终被拿鞫者。实由于两南监,兵使之状启。又曰。仍下天网恢恢。渠固难逃之教。夫奸澈为永庆所绝。常怀愤毒者久矣适当逆狱之起做成飞语自唱自和使其言传播远迩。监,兵使之状启。实由于此也。澈指永庆为三峰而请鞫。既鞫之后。自 上明知其无辜而特命放释。及阴嗾其徒党。启请再鞫。竟致瘦死狱中。此天下之至冤而国人所共知也。李成禄等徒知庇护私党。而不知公议之难掩。非但救浑。并与奸澈而救之。此邪论之所以横生。而浮诞之辈无所忌惮也。若非 圣上洞烛其情状。而使其说得行。则是非眩乱。公论晦塞。而国不可为国矣。岂可以事在既往而不为之追论哉。请李成禄,赵翊,闵有庆等。并 命罢职不叙。
顷在宪府处置。其时大司宪黄慎。因南儒文景虎上疏。避嫌之时。多费辞说。极其营救。至曰崔永庆之终被拿鞫者。实由于两南监,兵使之状启。又曰。仍下天网恢恢。渠固难逃之教。夫奸澈为永庆所绝。常怀愤毒者久矣适当逆狱之起做成飞语自唱自和使其言传播远迩。监,兵使之状启。实由于此也。澈指永庆为三峰而请鞫。既鞫之后。自 上明知其无辜而特命放释。及阴嗾其徒党。启请再鞫。竟致瘦死狱中。此天下之至冤而国人所共知也。李成禄等徒知庇护私党。而不知公议之难掩。非但救浑。并与奸澈而救之。此邪论之所以横生。而浮诞之辈无所忌惮也。若非 圣上洞烛其情状。而使其说得行。则是非眩乱。公论晦塞。而国不可为国矣。岂可以事在既往而不为之追论哉。请李成禄,赵翊,闵有庆等。并 命罢职不叙。答曰依启。其时传教云云之言。乃指其平日与郑贼相知之事而言。以其书札在故也。非指其元情也。此则台谏启辞中。亦有此意矣。但监,兵使因梁千顷等进告而状启。有人既告以逆贼。则为人臣者。将状启之乎。将掩置之乎。既闻其进告。则自当状启。既状启
隐峰全书卷二十六 第 2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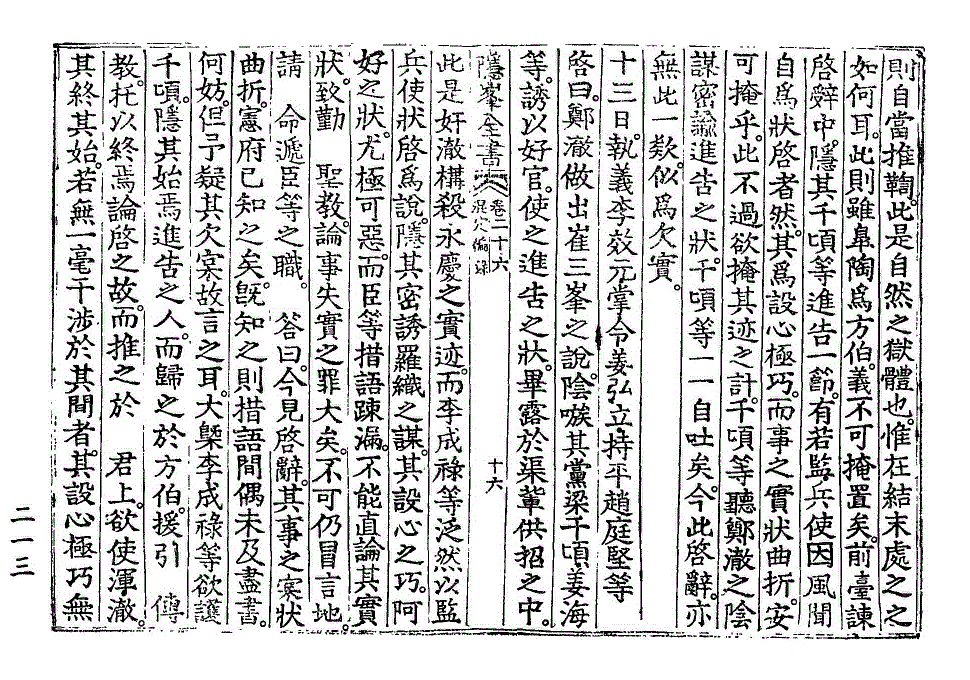 则自当推鞫。此是自然之狱体也。惟在结末处之之如何耳。此则虽皋陶为方伯。义不可掩置矣。前台谏启辞中。隐其千顷等进告一节。有若监,兵使因风闻自为状启者然。其为设心极巧。而事之实状曲折。安可掩乎。此不过欲掩其迹之计。千顷等听郑澈之阴谋密谕进告之状。千顷等一一自吐矣。今此启辞。亦无此一款。似为欠实。
则自当推鞫。此是自然之狱体也。惟在结末处之之如何耳。此则虽皋陶为方伯。义不可掩置矣。前台谏启辞中。隐其千顷等进告一节。有若监,兵使因风闻自为状启者然。其为设心极巧。而事之实状曲折。安可掩乎。此不过欲掩其迹之计。千顷等听郑澈之阴谋密谕进告之状。千顷等一一自吐矣。今此启辞。亦无此一款。似为欠实。十三日。执义李效元,掌令姜弘立,持平赵庭坚等 启曰。郑澈做出崔三峰之说。阴嗾其党梁千顷,姜海等。诱以好官。使之进告之状。毕露于渠辈供招之中。此是奸澈构杀永庆之实迹。而李成禄等泛然以监兵使状启为说。隐其密诱罗织之谋。其设心之巧。阿好之状。尤极可恶。而臣等措语疏漏。不能直论其实状。致勤 圣教。论事失实之罪大矣。不可仍冒言地。请 命递臣等之职。 答曰。今见启辞。其事之实状曲折。宪府已知之矣。既知之则措语间偶未及尽书。何妨。但予疑其欠实故言之耳。大槩李成禄等欲护千顷。隐其始焉进告之人。而归之于方伯。援引 传教。托以终焉论启之故。而推之于 君上。欲使浑,澈。其终其始。若无一毫干涉于其间者。其设心极巧无
隐峰全书卷二十六 第 2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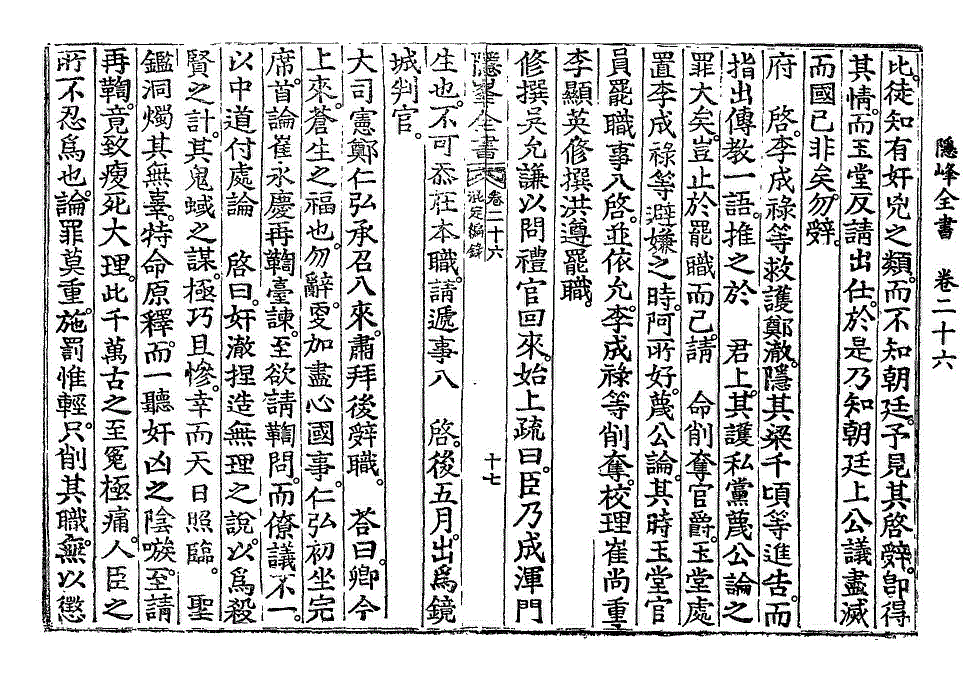 比。徒知有奸凶之类。而不知朝廷。予见其启辞。即得其情。而玉堂反请出仕。于是乃知朝廷上公议尽灭而国已非矣。勿辞。
比。徒知有奸凶之类。而不知朝廷。予见其启辞。即得其情。而玉堂反请出仕。于是乃知朝廷上公议尽灭而国已非矣。勿辞。府 启。李成禄等救护郑澈。隐其梁千顷等进告。而指出传教一语。推之于 君上。其护私党蔑公论之罪大矣。岂止于罢职而已。请 命削夺官爵。玉堂处置李成禄等避嫌之时。阿所好。蔑公论。其时玉堂官员罢职事入启。并依允。李成禄等削夺。校理崔尚重,李显英,修撰洪遵罢职。
修撰吴允谦以问礼官回来。始上疏曰。臣乃成浑门生也。不可忝在本职。请递事入 启。后五月。出为镜城判官。
大司宪郑仁弘承召入来。肃拜后辞职。 答曰。卿今上来。苍生之福也。勿辞。更加尽心国事。仁弘初坐完席。首论崔永庆再鞫台谏。至欲请鞫问。而僚议不一。以中道付处论 启曰。奸澈捏造无理之说。以为杀贤之计。其鬼蜮之谋。极巧且惨。幸而天日照临。 圣鉴洞烛其无辜。特命原释。而一听奸凶之阴嗾。至请再鞫。竟致瘦死大理。此千万古之至冤极痛。人臣之所不忍为也。论罪莫重。施罚惟轻。只削其职。无以惩
隐峰全书卷二十六 第 2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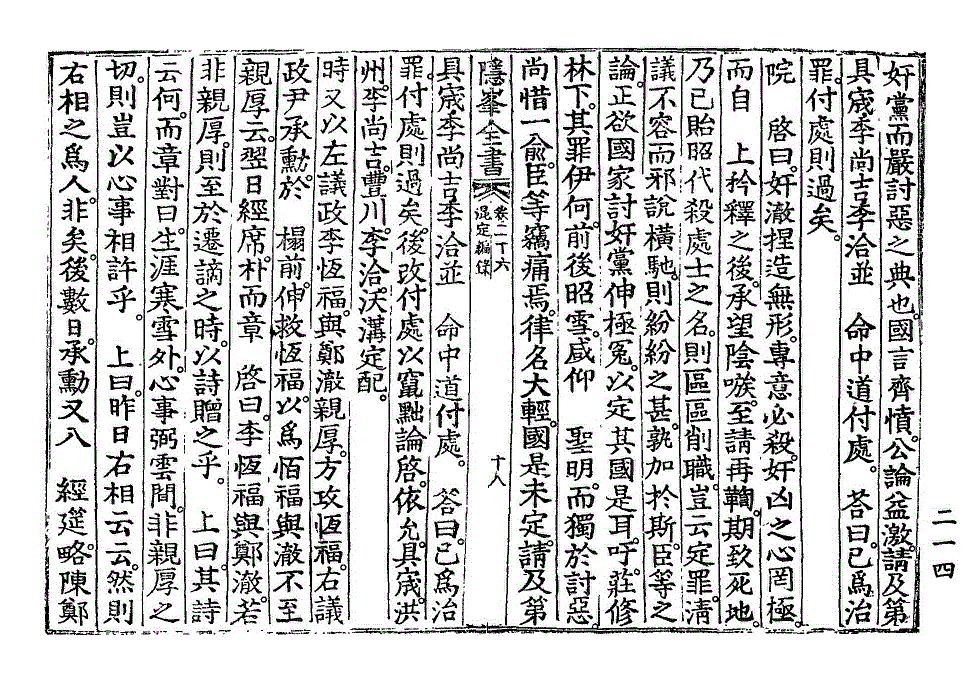 奸党而严讨恶之典也。国言齐愤。公论益激。请及第具宬,李尚吉,李洽并 命中道付处。 答曰。已为治罪。付处则过矣。
奸党而严讨恶之典也。国言齐愤。公论益激。请及第具宬,李尚吉,李洽并 命中道付处。 答曰。已为治罪。付处则过矣。院 启曰。奸澈捏造无形。专意必杀。奸凶之心罔极。而自 上矜释之后。承望阴嗾。至请再鞫。期致死地。乃已贻昭代杀处士之名。则区区削职。岂云定罪。清议不容而邪说横驰。则纷纷之甚。孰加于斯。臣等之论。正欲国家讨奸党伸极冤。以定其国是耳。吁。庄修林下。其罪伊何。前后昭雪。咸仰 圣明。而独于讨恶。尚惜一俞。臣等窃痛焉。律名大轻。国是未定。请及第具宬,李尚吉,李洽并 命中道付处。 答曰。已为治罪。付处则过矣。后改付处以窜黜论启。依允。具宬。洪州。李尚吉。丰川。李洽。沃沟定配。
时又以左议政李恒福。与郑澈亲厚。方攻恒福。右议政尹承勋。于 榻前。伸救恒福。以为恒福与澈不至亲厚云。翌日经席。朴而章 启曰。李恒福与郑澈。若非亲厚。则至于迁谪之时。以诗赠之乎。 上曰。其诗云何。而章对曰。生涯寒雪外。心事弼云间。非亲厚之切。则岂以心事相许乎。 上曰。昨日右相云云。然则右相之为人。非矣。后数日。承勋又入 经筵。略陈郑
隐峰全书卷二十六 第 2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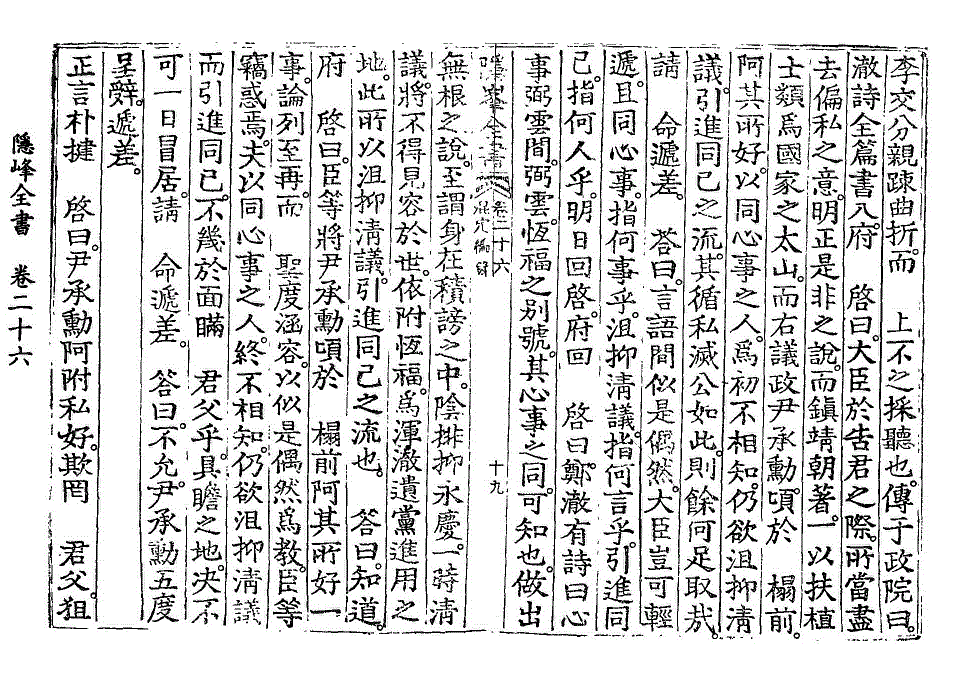 李交分亲疏曲折。而 上不之采听也。传于政院曰。澈诗全篇书入。府 启曰。大臣于告君之际。所当尽去偏私之意。明正是非之说。而镇靖朝著。一以扶植士类为国家之太山。而右议政尹承勋。顷于 榻前。阿其所好。以同心事之人。为初不相知。仍欲沮抑清议。引进同己之流。其循私灭公如此。则馀何足取哉。请 命递差。 答曰。言语间似是偶然。大臣岂可轻递。且同心事。指何事乎。沮抑清议。指何言乎。引进同己。指何人乎。明日回启。府回 启曰。郑澈有诗曰心事弼云间。弼云。恒福之别号。其心事之同。可知也。做出无根之说。至谓身在积谤之中。阴排抑永庆。一时清议。将不得见容于世。依附恒福。为浑,澈遗党进用之地。此所以沮抑清议。引进同己之流也。 答曰。知道。府 启曰。臣等将尹承勋顷于 榻前阿其所好一事。论列至再。而 圣度涵容。以似是偶然为教。臣等窃惑焉。夫以同心事之人。终不相知。仍欲沮抑清议而引进同己。不几于面瞒 君父乎。具瞻之地。决不可一日冒居。请 命递差。 答曰。不允。尹承勋五度呈辞。递差。
李交分亲疏曲折。而 上不之采听也。传于政院曰。澈诗全篇书入。府 启曰。大臣于告君之际。所当尽去偏私之意。明正是非之说。而镇靖朝著。一以扶植士类为国家之太山。而右议政尹承勋。顷于 榻前。阿其所好。以同心事之人。为初不相知。仍欲沮抑清议。引进同己之流。其循私灭公如此。则馀何足取哉。请 命递差。 答曰。言语间似是偶然。大臣岂可轻递。且同心事。指何事乎。沮抑清议。指何言乎。引进同己。指何人乎。明日回启。府回 启曰。郑澈有诗曰心事弼云间。弼云。恒福之别号。其心事之同。可知也。做出无根之说。至谓身在积谤之中。阴排抑永庆。一时清议。将不得见容于世。依附恒福。为浑,澈遗党进用之地。此所以沮抑清议。引进同己之流也。 答曰。知道。府 启曰。臣等将尹承勋顷于 榻前阿其所好一事。论列至再。而 圣度涵容。以似是偶然为教。臣等窃惑焉。夫以同心事之人。终不相知。仍欲沮抑清议而引进同己。不几于面瞒 君父乎。具瞻之地。决不可一日冒居。请 命递差。 答曰。不允。尹承勋五度呈辞。递差。正言朴楗 启曰。尹承勋阿附私好。欺罔 君父。狙
隐峰全书卷二十六 第 215L 页
 击重臣。图复党与。扶植亲交。沮抑清议之罪。不可不惩。臣于僚席之中。以当论言之。同僚不肯。臣之无状。言不见信。不可忝冒。请 命递职。 答曰。勿辞。退待物论。
击重臣。图复党与。扶植亲交。沮抑清议之罪。不可不惩。臣于僚席之中。以当论言之。同僚不肯。臣之无状。言不见信。不可忝冒。请 命递职。 答曰。勿辞。退待物论。大司谏权憘,献纳崔忠元 启曰。今日 经席中。正言朴楗欲论尹承勋。臣等之意。以为大臣若有大段过恶。则非但一司论之。虽三司并论可也。承勋所失。不过 榻前言语间差谬。其他罪状。臣等实未及闻知。宪府所论。则足惩其失。两司并论。事体重大。以此持难之际。楗立异遽起。臣等言不取信。势难相容。请命递臣等之职。 答曰。勿辞。退待物论。
司谏郑壳 启曰。论尹承勋事。臣之所见。与大司谏权憘等无异。不可处置同僚。请 命递臣职。 答曰。勿辞。退待物论。
大司宪郑仁弘,执义李效元,掌令赵廷坚等 启曰。臣等窃念右议政尹承勋 榻前之辞。近于面瞒 君父。沮抑清议。引进同己之计。不可谓言语间微失。故论列累日矣。今见大司谏权憘,司谏郑壳等避嫌。有曰不过言语间差谬。奄至于被劾。不可谓得中。臣等不敢自是己见。处置谏院。请递臣等之职。 答曰。
隐峰全书卷二十六 第 2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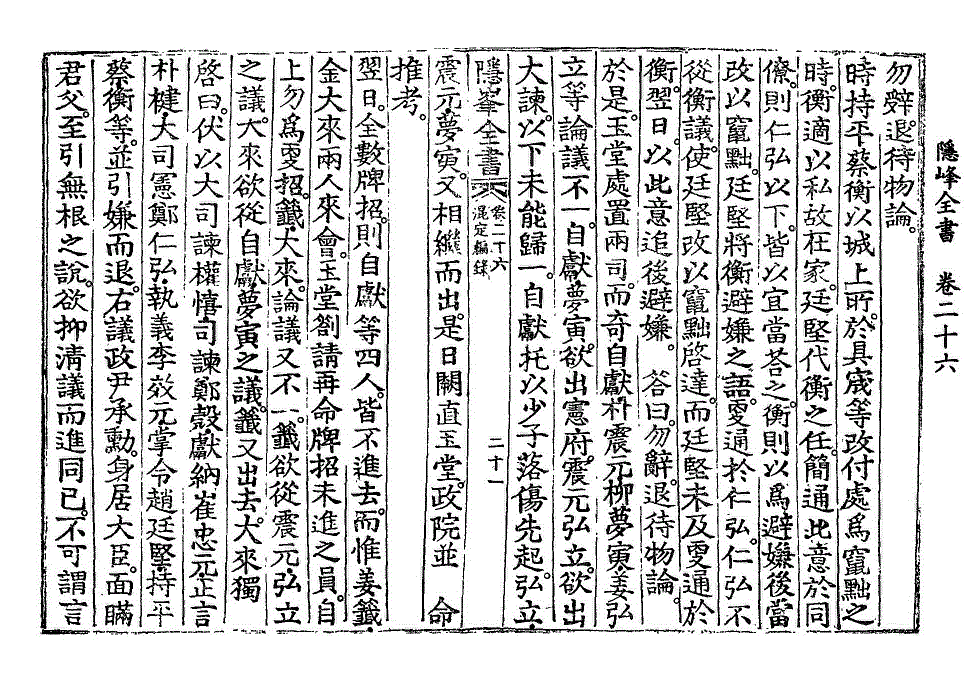 勿辞。退待物论。
勿辞。退待物论。时持平蔡衡以城上所。于具宬等改付处为窜黜之时。衡适以私故在家。廷坚代衡之任。简通此意于同僚。则仁弘以下。皆以宜当答之。衡则以为避嫌后当改以窜黜。廷坚将衡避嫌之语。更通于仁弘。仁弘不从衡议。使廷坚改以窜黜启达。而廷坚未及更通于衡。翌日。以此意追后避嫌。 答曰。勿辞。退待物论。
于是。玉堂处置两司。而奇自献,朴震元,柳梦寅,姜弘立等论议不一。自献,梦寅。欲出宪府。震元弘立。欲出大谏。以下未能归一。自献托以少子落伤先起。弘立,震元,梦寅。又相继而出。是日阙直玉堂。政院并 命推考。
翌日。全数牌招。则自献等四人。皆不进去。而惟姜签,金大来两人来会。玉堂劄请再命牌招未进之员。自上勿为更招。签,大来。论议又不一。签欲从震元,弘立之议。大来欲从自献,梦寅之议。签又出去。大来独 启曰。伏以大司谏权憘,司谏郑壳,献纳崔忠元,正言朴楗,大司宪郑仁弘,执义李效元,掌令赵廷坚,持平蔡衡等。并引嫌而退。右议政尹承勋。身居大臣。面瞒君父。至引无根之说。欲抑清议而进同己。不可谓言
隐峰全书卷二十六 第 2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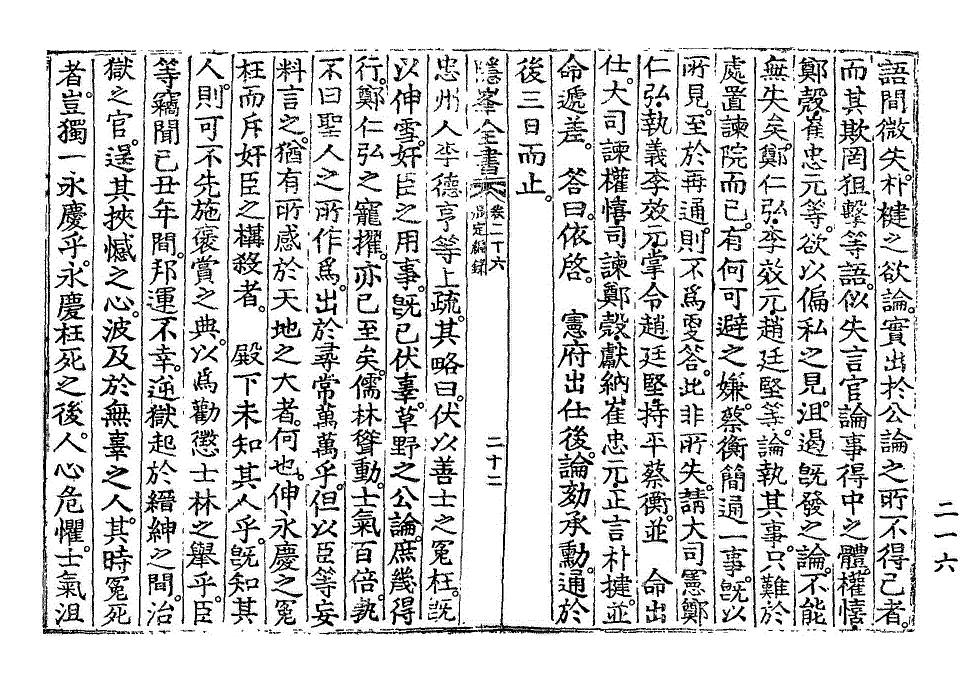 语间微失。朴楗之欲论。实出于公论之所不得已者。而其欺罔狙击等语。似失言官论事得中之体。权憘,郑壳,崔忠元等。欲以偏私之见。沮遏既发之论。不能无失矣。郑仁弘,李效元,赵廷坚等。论执其事。只难于处直谏院而已。有何可避之嫌。蔡衡简通一事。既以所见。至于再通。则不为更答。此非所失。请大司宪郑仁弘,执义李效元,掌令赵廷坚,持平蔡衡。并 命出仕。大司谏权憘,司谏郑壳,献纳崔忠元,正言朴楗。并命递差。 答曰。依启。 宪府出仕后。论劾承勋。通于后三日而止。
语间微失。朴楗之欲论。实出于公论之所不得已者。而其欺罔狙击等语。似失言官论事得中之体。权憘,郑壳,崔忠元等。欲以偏私之见。沮遏既发之论。不能无失矣。郑仁弘,李效元,赵廷坚等。论执其事。只难于处直谏院而已。有何可避之嫌。蔡衡简通一事。既以所见。至于再通。则不为更答。此非所失。请大司宪郑仁弘,执义李效元,掌令赵廷坚,持平蔡衡。并 命出仕。大司谏权憘,司谏郑壳,献纳崔忠元,正言朴楗。并命递差。 答曰。依启。 宪府出仕后。论劾承勋。通于后三日而止。忠州人李德亨等上疏。其略曰。伏以善士之冤枉。既以伸雪。奸臣之用事。既已伏辜。草野之公论。庶几得行。郑仁弘之宠擢。亦已至矣。儒林耸动。士气百倍。孰不曰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乎。但以臣等妄料言之。犹有所感于天地之大者。何也。伸永庆之冤枉而斥奸臣之构杀者。 殿下未知其人乎。既知其人。则可不先施褒赏之典。以为劝惩士林之举乎。臣等窃闻己丑年间。邦运不辛。逆狱起于缙绅之间。治狱之官。逞其挟憾之心。波及于无辜之人。其时冤死者。岂独一永庆乎。永庆枉死之后。人心危惧。士气沮
隐峰全书卷二十六 第 2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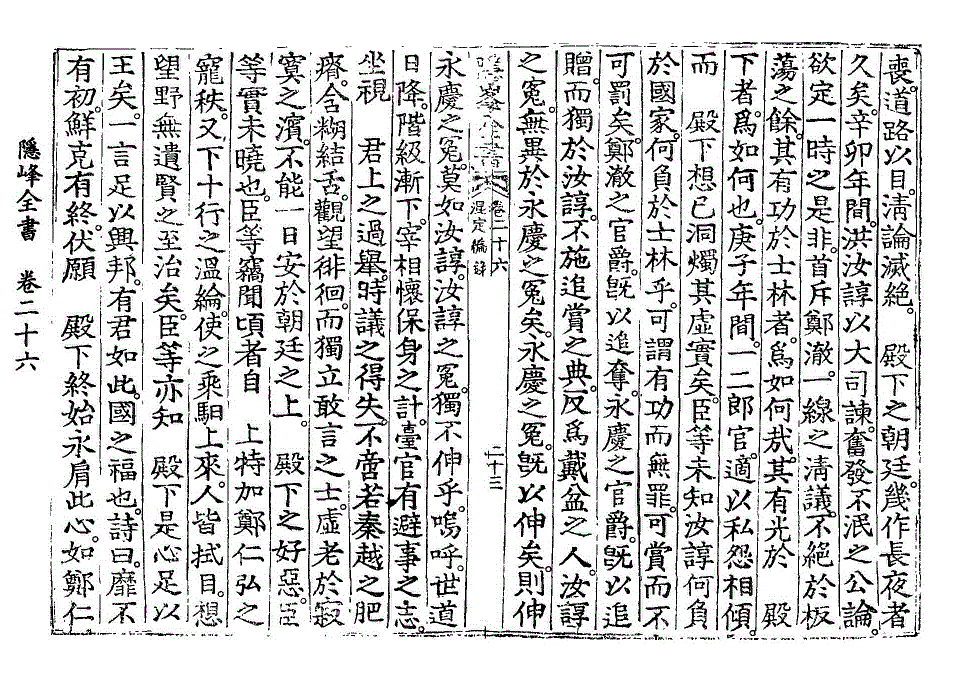 丧。道路以目。清论灭绝。 殿下之朝廷。几作长夜者久矣。辛卯年间。洪汝谆以大司谏。奋发不泯之公论。欲定一时之是非。首斥郑澈。一线之清议。不绝于板荡之馀。其有功于士林者。为如何哉。其有光于 殿下者。为如何也。庚子年间。一二郎官。适以私怨相倾。而 殿下想已洞烛其虚实矣。臣等未知汝谆何负于国家。何负于士林乎。可谓有功而无罪。可赏而不可罚矣。郑澈之官爵。既以追夺。永庆之官爵。既以追赠。而独于汝谆。不施追赏之典。反为戴盆之人。汝谆之冤。无异于永庆之冤矣。永庆之冤。既以伸矣。则伸永庆之冤。莫如汝谆。汝谆之冤。独不伸乎。呜呼。世道日降。阶级渐下。宰相怀保身之计。台官有避事之志。坐视 君上之过举。时议之得失。不啻若秦越之肥瘠。含糊结舌。观望徘徊。而独立敢言之士。虚老于寂寞之滨。不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 殿下之好恶。臣等实未晓也。臣等窃闻顷者自 上特加郑仁弘之宠秩。又下十行之温纶。使之乘驲上来。人皆拭目。想望野无遗贤之至治矣。臣等亦知 殿下是心足以王矣。一言足以兴邦。有君如此。国之福也。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伏愿 殿下终始永肩此心。如郑仁
丧。道路以目。清论灭绝。 殿下之朝廷。几作长夜者久矣。辛卯年间。洪汝谆以大司谏。奋发不泯之公论。欲定一时之是非。首斥郑澈。一线之清议。不绝于板荡之馀。其有功于士林者。为如何哉。其有光于 殿下者。为如何也。庚子年间。一二郎官。适以私怨相倾。而 殿下想已洞烛其虚实矣。臣等未知汝谆何负于国家。何负于士林乎。可谓有功而无罪。可赏而不可罚矣。郑澈之官爵。既以追夺。永庆之官爵。既以追赠。而独于汝谆。不施追赏之典。反为戴盆之人。汝谆之冤。无异于永庆之冤矣。永庆之冤。既以伸矣。则伸永庆之冤。莫如汝谆。汝谆之冤。独不伸乎。呜呼。世道日降。阶级渐下。宰相怀保身之计。台官有避事之志。坐视 君上之过举。时议之得失。不啻若秦越之肥瘠。含糊结舌。观望徘徊。而独立敢言之士。虚老于寂寞之滨。不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 殿下之好恶。臣等实未晓也。臣等窃闻顷者自 上特加郑仁弘之宠秩。又下十行之温纶。使之乘驲上来。人皆拭目。想望野无遗贤之至治矣。臣等亦知 殿下是心足以王矣。一言足以兴邦。有君如此。国之福也。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伏愿 殿下终始永肩此心。如郑仁隐峰全书卷二十六 第 2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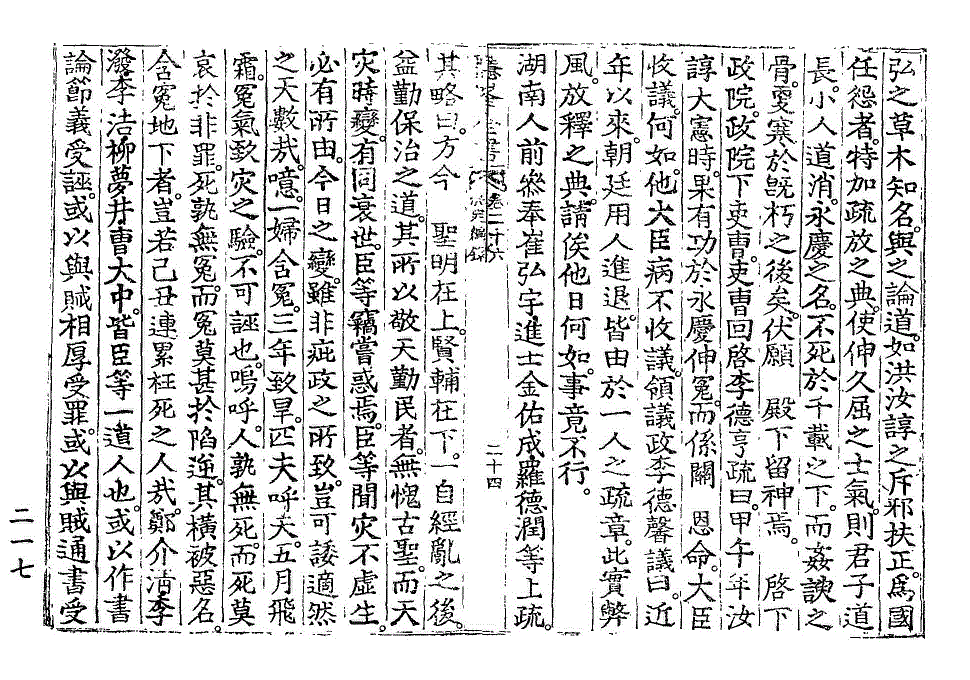 弘之草木知名。与之论道。如洪汝谆之斥邪扶正。为国任怨者。特加疏放之典。使伸久屈之士气。则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永庆之名。不死于千载之下。而奸谀之骨。更寒于既朽之后矣。伏愿 殿下留神焉。 启下政院。政院下吏曹。吏曹回启李德亨疏曰。甲午年汝谆大宪时。果有功于永庆伸冤。而系关 恩命。大臣收议。何如。他大臣病不收议。领议政李德声议曰。近年以来。朝廷用人进退。皆由于一人之疏章。此实弊风。放释之典。请俟他日何如。事竟不行。
弘之草木知名。与之论道。如洪汝谆之斥邪扶正。为国任怨者。特加疏放之典。使伸久屈之士气。则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永庆之名。不死于千载之下。而奸谀之骨。更寒于既朽之后矣。伏愿 殿下留神焉。 启下政院。政院下吏曹。吏曹回启李德亨疏曰。甲午年汝谆大宪时。果有功于永庆伸冤。而系关 恩命。大臣收议。何如。他大臣病不收议。领议政李德声议曰。近年以来。朝廷用人进退。皆由于一人之疏章。此实弊风。放释之典。请俟他日何如。事竟不行。湖南人前参奉崔弘宇,进士金佑成,罗德润等上疏。其略曰。方今 圣明在上。贤辅在下。一自经乱之后。益勤保治之道。其所以敬天勤民者。无愧古圣。而天灾时变。有同衰世。臣等窃尝惑焉。臣等闻灾不虚生。必有所由。今日之变。虽非疵政之所致。岂可诿适然之天数哉。噫。一妇含冤。三年致旱。匹夫呼夫。五月飞霜。冤气致灾之验。不可诬也。呜呼。人孰无死。而死莫哀于非罪。死孰无冤。而冤莫甚于陷逆。其横被恶名。含冤地下者。岂若己丑连累枉死之人哉。郑介清,李泼,李洁,柳梦井,曹大中。皆臣等一道人也。或以作书论节义受诬。或以与贼相厚受罪。或以与贼通书受
隐峰全书卷二十六 第 2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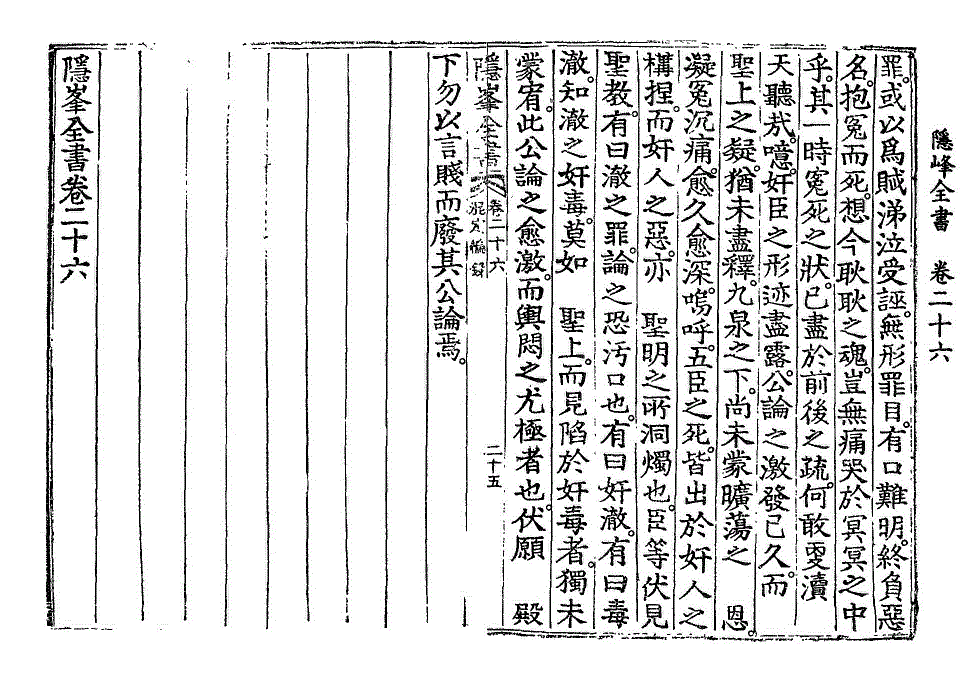 罪。或以为贼涕泣受诬。无形罪目。有口难明。终负恶名。抱冤而死。想今耿耿之魂。岂无痛哭于冥冥之中乎。其一时冤死之状。已尽于前后之疏。何敢更渎 天听哉。噫。奸臣之形迹尽露。公论之激发已久。而 圣上之疑。犹未尽释。九泉之下。尚未蒙旷荡之 恩。凝冤沈痛。愈久愈深。呜呼。五臣之死。皆出于奸人之构捏。而奸人之恶。亦 圣明之所洞烛也。臣等伏见圣教。有曰澈之罪。论之恐污口也。有曰奸澈。有曰毒澈。知澈之奸毒。莫如 圣上。而见陷于奸毒者。独未蒙宥。此公论之愈激。而舆闷之尤极者也。伏愿 殿下勿以言贱而废其公论焉。
罪。或以为贼涕泣受诬。无形罪目。有口难明。终负恶名。抱冤而死。想今耿耿之魂。岂无痛哭于冥冥之中乎。其一时冤死之状。已尽于前后之疏。何敢更渎 天听哉。噫。奸臣之形迹尽露。公论之激发已久。而 圣上之疑。犹未尽释。九泉之下。尚未蒙旷荡之 恩。凝冤沈痛。愈久愈深。呜呼。五臣之死。皆出于奸人之构捏。而奸人之恶。亦 圣明之所洞烛也。臣等伏见圣教。有曰澈之罪。论之恐污口也。有曰奸澈。有曰毒澈。知澈之奸毒。莫如 圣上。而见陷于奸毒者。独未蒙宥。此公论之愈激。而舆闷之尤极者也。伏愿 殿下勿以言贱而废其公论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