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第 x 页
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混定编录(前集)
混定编录(前集)
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第 1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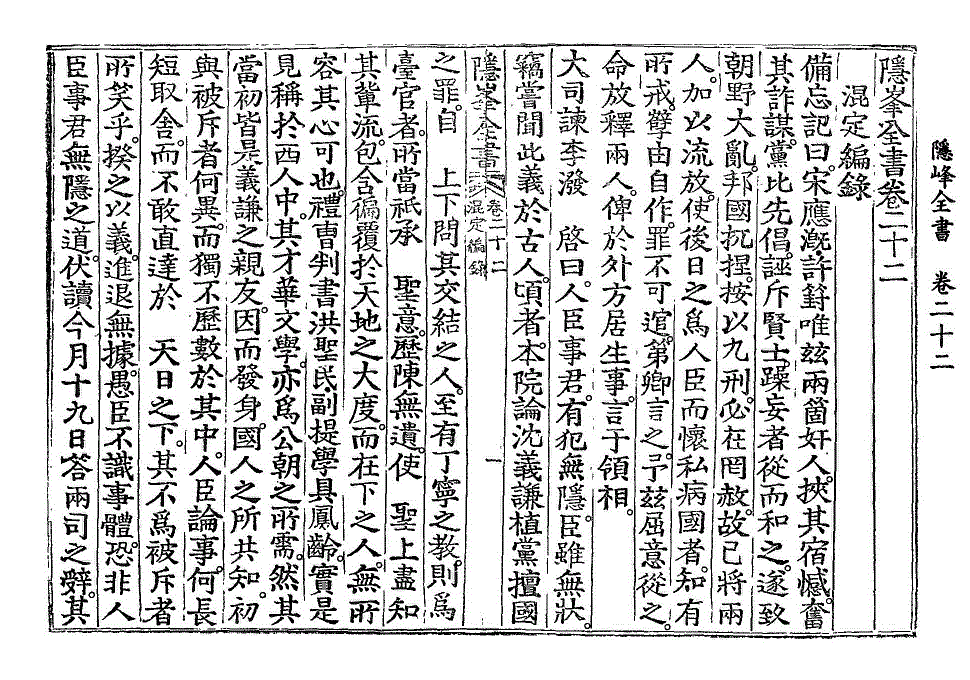 [宣庙朝]
[宣庙朝]备忘记曰。宋应溉,许篈唯兹两个奸人。挟其宿憾。奋其诈谋。党比先倡。诬斥贤士。躁妄者从而和之。遂致朝野大乱。邦国扤捏。按以九刑。必在罔赦。故已将两人。加以流放。使后日之为人臣而怀私病国者。知有所戒。孽由自作。罪不可逭。第卿言之。予兹屈意从之。命放释两人。俾于外方居生事。言于领相。
大司谏李泼 启曰。人臣事君。有犯无隐。臣虽无状。窃尝闻此义于古人。顷者。本院论沈义谦植党擅国之罪。自 上下问其交结之人。至有丁宁之教。则为台官者。所当祗承 圣意。历陈无遗。使 圣上尽知其辈流。包含遍覆于天地之大度。而在下之人。无所容其心可也。礼曹判书洪圣民,副提学具凤龄。实是见称于西人中。其才华文学。亦为公朝之所需。然其当初皆是义谦之亲友。因而发身。国人之所共知。初与被斥者何异。而独不历数于其中。人臣论事。何长短取舍。而不敢直达于 天日之下。其不为被斥者所笑乎。揆之以义。进退无据。愚臣不识事体。恐非人臣事君无隐之道。伏读今月十九日答两司之辞。其
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第 1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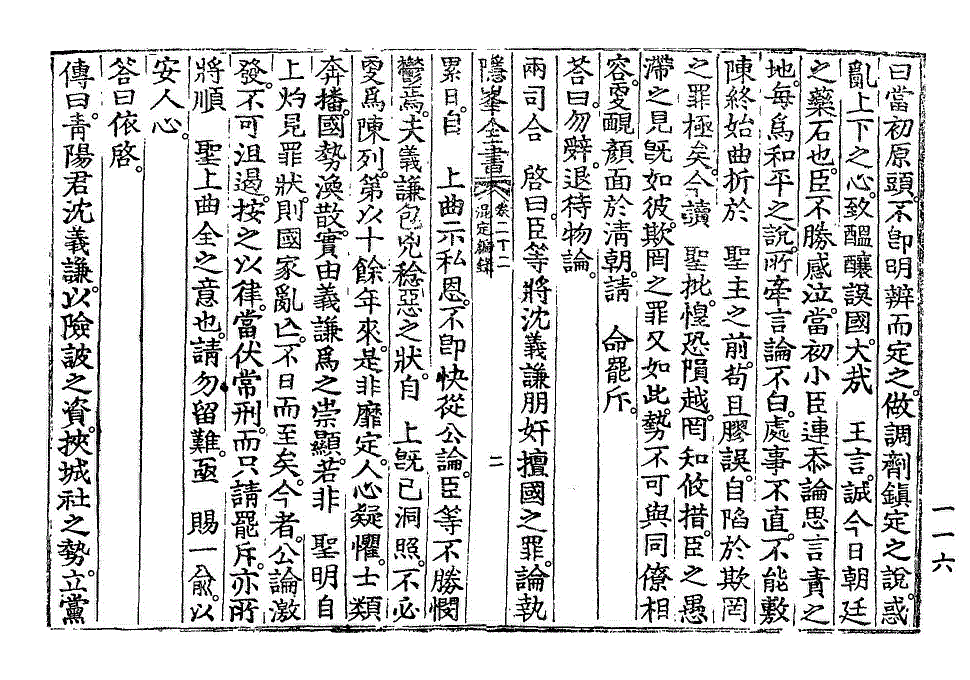 曰当初原头。不即明辨而定之。做调剂镇定之说。惑乱上下之心。致酝酿误国。大哉 王言。诚今日朝廷之药石也。臣不胜感泣。当初小臣连忝论思言责之地。每为和平之说。所牵言论不白。处事不直。不能敷陈终始曲折于 圣主之前。苟且胶误。自陷于欺罔之罪极矣。今读 圣批。惶恐陨越。罔知攸措。臣之愚滞之见既如彼。欺罔之罪又如此。势不可与同僚相容。更腼颜面于清朝。请 命罢斥。
曰当初原头。不即明辨而定之。做调剂镇定之说。惑乱上下之心。致酝酿误国。大哉 王言。诚今日朝廷之药石也。臣不胜感泣。当初小臣连忝论思言责之地。每为和平之说。所牵言论不白。处事不直。不能敷陈终始曲折于 圣主之前。苟且胶误。自陷于欺罔之罪极矣。今读 圣批。惶恐陨越。罔知攸措。臣之愚滞之见既如彼。欺罔之罪又如此。势不可与同僚相容。更腼颜面于清朝。请 命罢斥。答曰。勿辞。退待物论。
两司合 启曰。臣等将沈义谦朋奸擅国之罪。论执累日。自 上曲示私恩。不即快从公论。臣等不胜悯郁焉。夫义谦包凶稔恶之状。自 上既已洞照。不必更为陈列。第以十馀年来。是非靡定。人心疑惧。士类奔播。国势涣散。实由义谦为之崇显。若非 圣明自上灼见罪状。则国家乱亡。不日而至矣。今者。公论激发。不可沮遏。按之以律。当伏常刑。而只请罢斥。亦所将顺 圣上曲全之意也。请勿留难。亟 赐一俞。以安人心。
答曰依启。
传曰。青阳君沈义谦。以险诐之资。挟城社之势。立党
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第 1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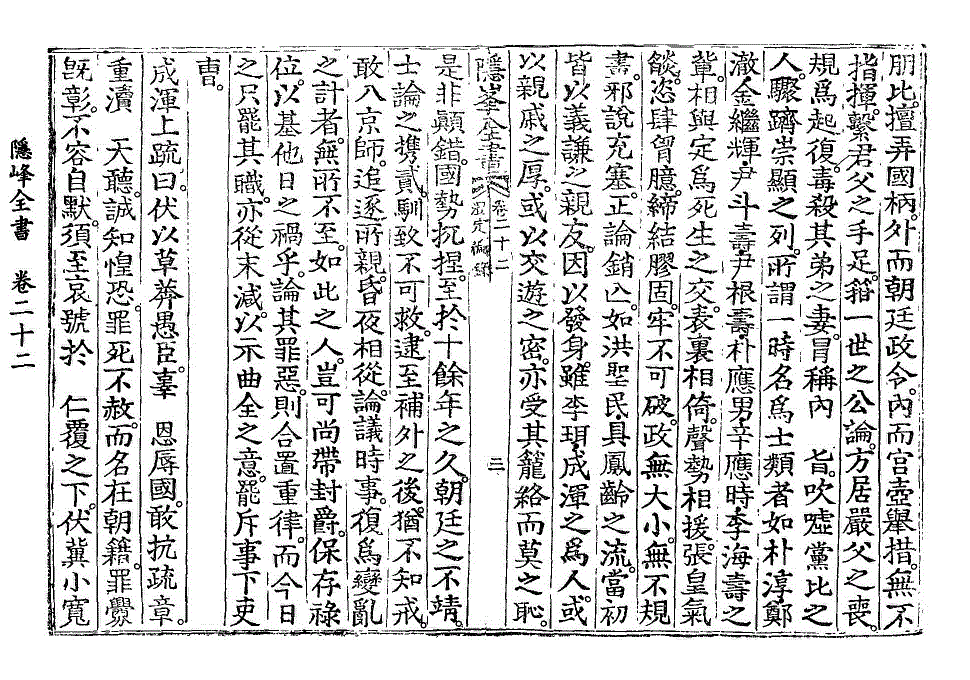 朋比。擅弄国柄。外而朝廷政令。内而宫壶举措。无不指挥。系君父之手足。钳一世之公论。方居严父之丧。规为起复。毒杀其弟之妻。冒称内 旨。吹嘘党比之人。骤跻崇显之列。所谓一时名为士类者如朴淳,郑澈,金继辉,尹斗寿,尹根寿,朴应男,辛应时,李海寿之辈。相与定为死生之交。表里相倚。声势相援。张皇气焰。恣肆胸臆。缔结胶固。牢不可破。政无大小。无不规画。邪说充塞。正论销亡。如洪圣民,具凤龄之流。当初皆以义谦之亲友。因以发身。虽李珥,成浑之为人。或以亲戚之厚。或以交游之密。亦受其笼络而莫之耻。是非颠错。国势扤捏。至于十馀年之久。朝廷之不靖。士论之携贰。驯致不可救。逮至补外之后。犹不知戒。敢入京师。追逐所亲。昏夜相从。论议时事。复为变乱之计者。无所不至。如此之人。岂可尚带封爵。保存禄位。以基他日之祸乎。论其罪恶。则合置重律。而今日之只罢其职。亦从末减。以示曲全之意。罢斥事下吏曹。
朋比。擅弄国柄。外而朝廷政令。内而宫壶举措。无不指挥。系君父之手足。钳一世之公论。方居严父之丧。规为起复。毒杀其弟之妻。冒称内 旨。吹嘘党比之人。骤跻崇显之列。所谓一时名为士类者如朴淳,郑澈,金继辉,尹斗寿,尹根寿,朴应男,辛应时,李海寿之辈。相与定为死生之交。表里相倚。声势相援。张皇气焰。恣肆胸臆。缔结胶固。牢不可破。政无大小。无不规画。邪说充塞。正论销亡。如洪圣民,具凤龄之流。当初皆以义谦之亲友。因以发身。虽李珥,成浑之为人。或以亲戚之厚。或以交游之密。亦受其笼络而莫之耻。是非颠错。国势扤捏。至于十馀年之久。朝廷之不靖。士论之携贰。驯致不可救。逮至补外之后。犹不知戒。敢入京师。追逐所亲。昏夜相从。论议时事。复为变乱之计者。无所不至。如此之人。岂可尚带封爵。保存禄位。以基他日之祸乎。论其罪恶。则合置重律。而今日之只罢其职。亦从末减。以示曲全之意。罢斥事下吏曹。成浑上疏曰。伏以草莽愚臣。辜 恩辱国。敢抗疏章。重渎 天听。诚知惶恐。罪死不赦。而名在朝籍。罪衅既彰。不容自默。须至哀号于 仁覆之下。伏冀小宽
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第 1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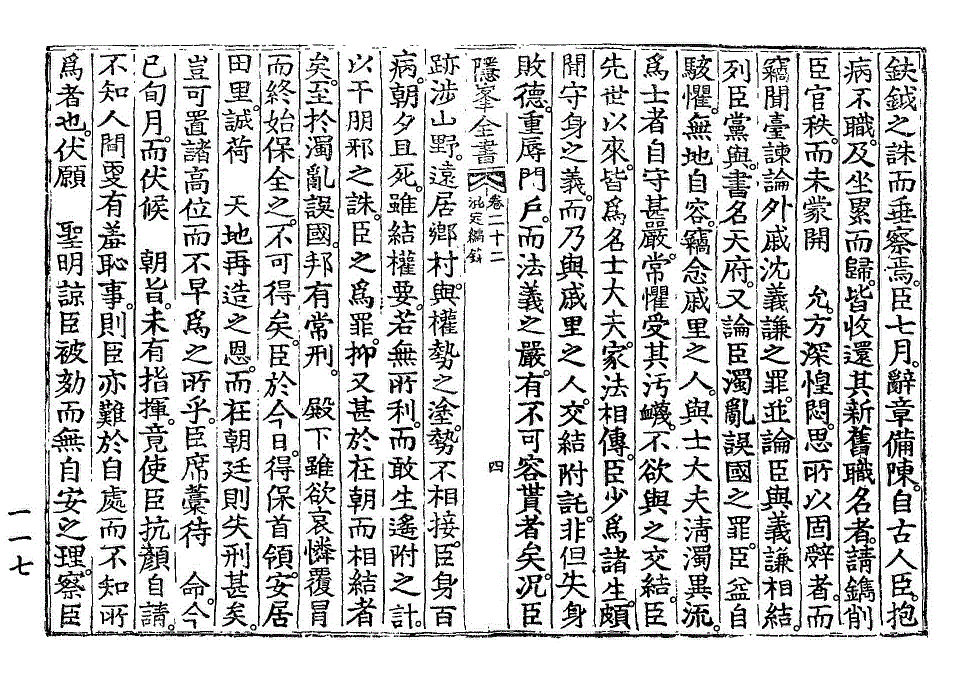 鈇钺之诛而垂察焉。臣七月。辞章备陈。自古人臣。抱病不职。及坐累而归。皆收还其新旧职名者。请镌削臣官秩。而未蒙开 允。方深惶闷。思所以固辞者。而窃闻台谏论外戚沈义谦之罪。并论臣与义谦相结。列臣党与。书名天府。又论臣浊乱误国之罪。臣益自骇惧。无地自容。窃念戚里之人。与士大夫清浊异流。为士者自守甚严。常惧受其污蔑。不欲与之交结。臣先世以来。皆为名士大夫。家法相传。臣少为诸生。颇闻守身之义。而乃与戚里之人。交结附托。非但失身败德。重辱门户。而法义之严。有不可容贳者矣。况臣迹涉山野。远居乡村。与权势之涂。势不相接。臣身百病。朝夕且死。虽结权要。若无所利。而敢生遥附之计。以干朋邪之诛。臣之为罪。抑又甚于在朝而相结者矣。至于浊乱误国。邦有常刑。 殿下虽欲哀怜覆冒而终始保全之。不可得矣。臣于今日。得保首领。安居田里。诚荷 天地再造之恩。而在朝廷则失刑甚矣。岂可置诸高位而不早为之所乎。臣席藁待 命。今已旬月。而伏候 朝旨。未有指挥。竟使臣抗颜自请。不知人间更有羞耻事。则臣亦难于自处而不知所为者也。伏愿 圣明谅臣被劾而无自安之理。察臣
鈇钺之诛而垂察焉。臣七月。辞章备陈。自古人臣。抱病不职。及坐累而归。皆收还其新旧职名者。请镌削臣官秩。而未蒙开 允。方深惶闷。思所以固辞者。而窃闻台谏论外戚沈义谦之罪。并论臣与义谦相结。列臣党与。书名天府。又论臣浊乱误国之罪。臣益自骇惧。无地自容。窃念戚里之人。与士大夫清浊异流。为士者自守甚严。常惧受其污蔑。不欲与之交结。臣先世以来。皆为名士大夫。家法相传。臣少为诸生。颇闻守身之义。而乃与戚里之人。交结附托。非但失身败德。重辱门户。而法义之严。有不可容贳者矣。况臣迹涉山野。远居乡村。与权势之涂。势不相接。臣身百病。朝夕且死。虽结权要。若无所利。而敢生遥附之计。以干朋邪之诛。臣之为罪。抑又甚于在朝而相结者矣。至于浊乱误国。邦有常刑。 殿下虽欲哀怜覆冒而终始保全之。不可得矣。臣于今日。得保首领。安居田里。诚荷 天地再造之恩。而在朝廷则失刑甚矣。岂可置诸高位而不早为之所乎。臣席藁待 命。今已旬月。而伏候 朝旨。未有指挥。竟使臣抗颜自请。不知人间更有羞耻事。则臣亦难于自处而不知所为者也。伏愿 圣明谅臣被劾而无自安之理。察臣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第 1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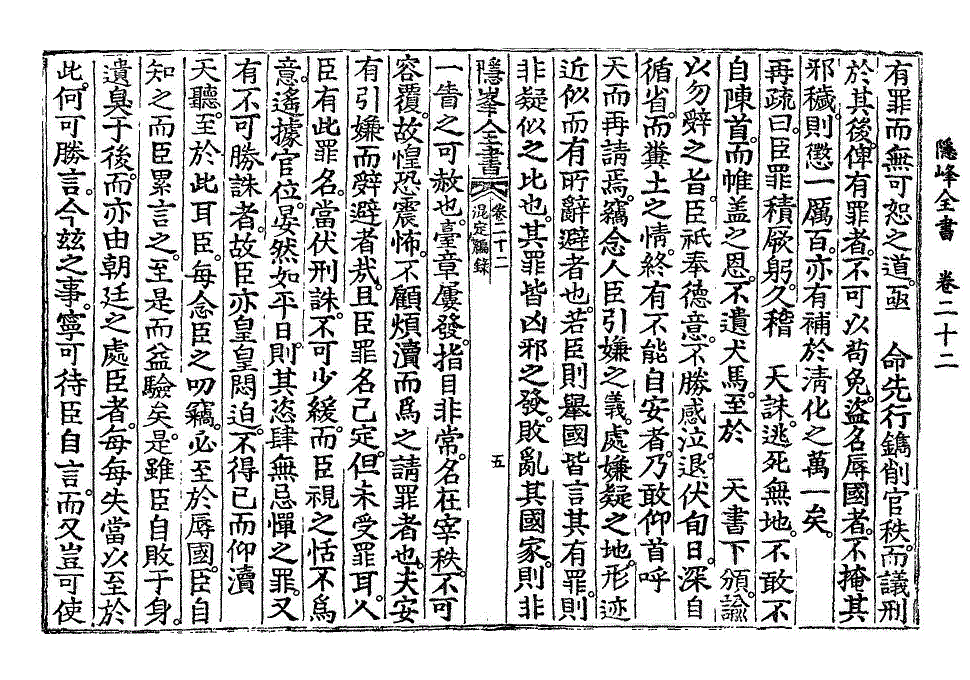 有罪而无可恕之道。亟 命先行镌削官秩。而议刑于其后。俾有罪者。不可以苟免。盗名辱国者。不掩其邪秽。则惩一厉百。亦有补于清化之万一矣。
有罪而无可恕之道。亟 命先行镌削官秩。而议刑于其后。俾有罪者。不可以苟免。盗名辱国者。不掩其邪秽。则惩一厉百。亦有补于清化之万一矣。再疏曰。臣罪积厥躬。久稽 天诛。逃死无地。不敢不自陈首。而帷盖之恩。不遗犬马。至于 天书下颁。谕以勿辞之旨。臣祗奉德意。不胜感泣。退伏旬日。深自循省。而粪土之情。终有不能自安者。乃敢仰首呼 天而再请焉。窃念人臣引嫌之义。处嫌疑之地。形迹近似而有所辞避者也。若臣则举国皆言其有罪。则非疑似之比也。其罪皆凶邪之发。败乱其国家。则非一眚之可赦也。台章屡发。指目非常。名在宰秩。不可容覆。故惶恐震怖。不顾烦渎而为之请罪者也。夫安有引嫌而辞避者哉。且臣罪名已定。但未受罪耳。人臣有此罪名。当伏刑诛。不可少缓。而臣视之恬不为意。遥据官位。晏然如平日。则其恣肆无忌惮之罪。又有不可胜诛者。故臣亦皇皇闷迫。不得已而仰渎 天听。至于此耳臣。每念臣之叨窃。必至于辱国。臣自知之而臣累言之。至是而益验矣。是虽臣自败于身。遗臭于后。而亦由朝廷之处臣者。每每失当以至于此。何可胜言。今兹之事。宁可待臣自言。而又岂可使
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第 1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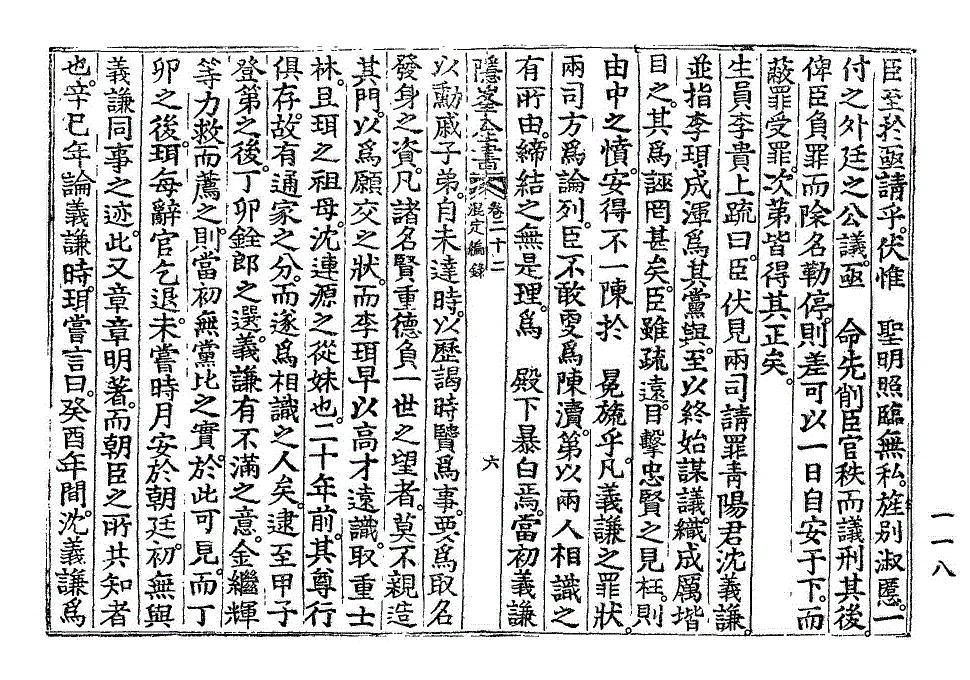 臣至于亟请乎。伏惟 圣明照临无私。旌别淑慝。一付之外廷之公议。亟 命先削臣官秩而议刑其后。俾臣负罪而除名勒停。则差可以一日自安于下。而蔽罪受罪。次第皆得其正矣。
臣至于亟请乎。伏惟 圣明照临无私。旌别淑慝。一付之外廷之公议。亟 命先削臣官秩而议刑其后。俾臣负罪而除名勒停。则差可以一日自安于下。而蔽罪受罪。次第皆得其正矣。生员李贵上疏曰。臣伏见两司请罪青阳君沈义谦。并指李珥,成浑为其党与。至以终始谋议。织成厉阶目之。其为诬罔甚矣。臣虽疏远。目击忠贤之见枉。则由中之愤。安得不一陈于 冕旒乎。凡义谦之罪状。两司方为论列。臣不敢更为陈渎。第以两人相识之有所由。缔结之无是理。为 殿下暴白焉。当初义谦以勋戚子弟。自未达时。以历谒时贤为事。要为取名发身之资。凡诸名贤重德负一世之望者。莫不亲造其门。以为愿交之状。而李珥早以高才远识。取重士林。且珥之祖母。沈连源之从妹也。二十年前。其尊行俱存。故有通家之分。而遂为相识之人矣。逮至甲子登第之后。丁卯铨郎之选。义谦有不满之意。金继辉等力救而荐之。则当初无党比之实。于此可见。而丁卯之后。珥每辞官乞退。未尝时月安于朝廷。初无与义谦同事之迹。此又章章明著。而朝臣之所共知者也。辛巳年论义谦时。珥尝言曰。癸酉年间。沈义谦为
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第 1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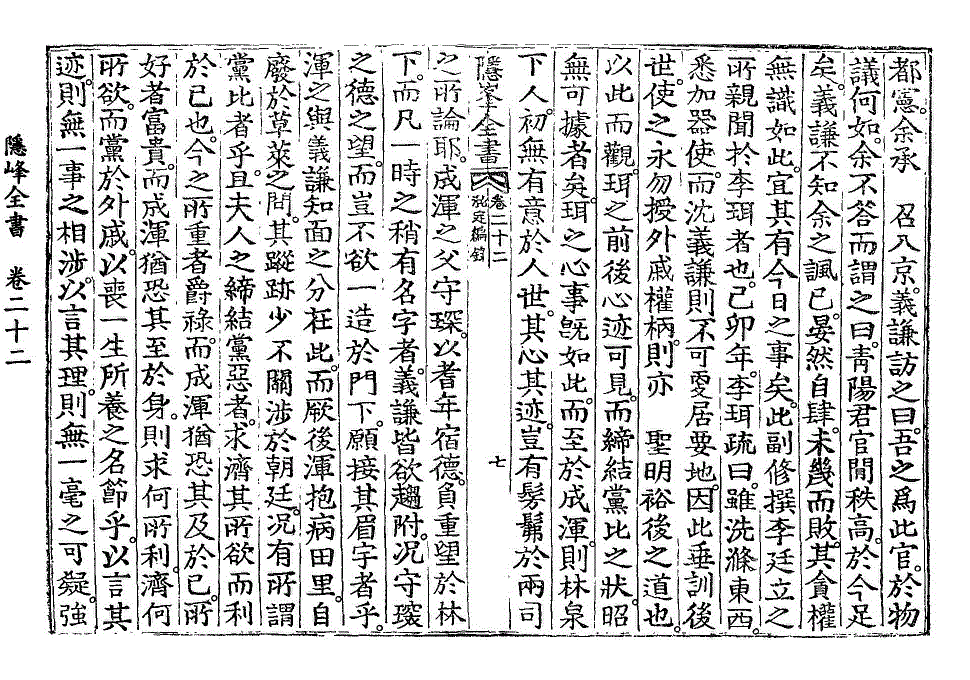 都宪。余承 召入京。义谦访之曰。吾之为此官。于物议何如。余不答而谓之曰。青阳君官閒秩高。于今足矣。义谦不知余之讽已。晏然自肆。未几而败。其贪权无识如此。宜其有今日之事矣。此副修撰李廷立之所亲闻于李珥者也。己卯年。李珥疏曰。虽洗涤东西。悉加器使。而沈义谦则不可更居要地。因此垂训后世。使之永勿授外戚权柄。则亦 圣明裕后之道也。以此而观。珥之前后心迹可见。而缔结党比之状。昭无可据者矣。珥之心事既如此。而至于成浑。则林泉下人。初无有意于人世。其心其迹。岂有髣髴于两司之所论耶。成浑之父守琛。以耆年宿德。负重望于林下。而凡一时之稍有名字者。义谦皆欲趋附。况守琛之德之望。而岂不欲一造于门下。愿接其眉宇者乎。浑之与义谦知面之分在此。而厥后浑抱病田里。自废于草莱之间。其踪迹少不关涉于朝廷。况有所谓党比者乎。且夫人之缔结党恶者。求济其所欲而利于己也。今之所重者爵禄。而成浑犹恐其及于己。所好者富贵。而成浑犹恐其至于身。则求何所利。济何所欲。而党于外戚。以丧一生所养之名节乎。以言其迹。则无一事之相涉。以言其理。则无一毫之可疑。强
都宪。余承 召入京。义谦访之曰。吾之为此官。于物议何如。余不答而谓之曰。青阳君官閒秩高。于今足矣。义谦不知余之讽已。晏然自肆。未几而败。其贪权无识如此。宜其有今日之事矣。此副修撰李廷立之所亲闻于李珥者也。己卯年。李珥疏曰。虽洗涤东西。悉加器使。而沈义谦则不可更居要地。因此垂训后世。使之永勿授外戚权柄。则亦 圣明裕后之道也。以此而观。珥之前后心迹可见。而缔结党比之状。昭无可据者矣。珥之心事既如此。而至于成浑。则林泉下人。初无有意于人世。其心其迹。岂有髣髴于两司之所论耶。成浑之父守琛。以耆年宿德。负重望于林下。而凡一时之稍有名字者。义谦皆欲趋附。况守琛之德之望。而岂不欲一造于门下。愿接其眉宇者乎。浑之与义谦知面之分在此。而厥后浑抱病田里。自废于草莱之间。其踪迹少不关涉于朝廷。况有所谓党比者乎。且夫人之缔结党恶者。求济其所欲而利于己也。今之所重者爵禄。而成浑犹恐其及于己。所好者富贵。而成浑犹恐其至于身。则求何所利。济何所欲。而党于外戚。以丧一生所养之名节乎。以言其迹。则无一事之相涉。以言其理。则无一毫之可疑。强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第 1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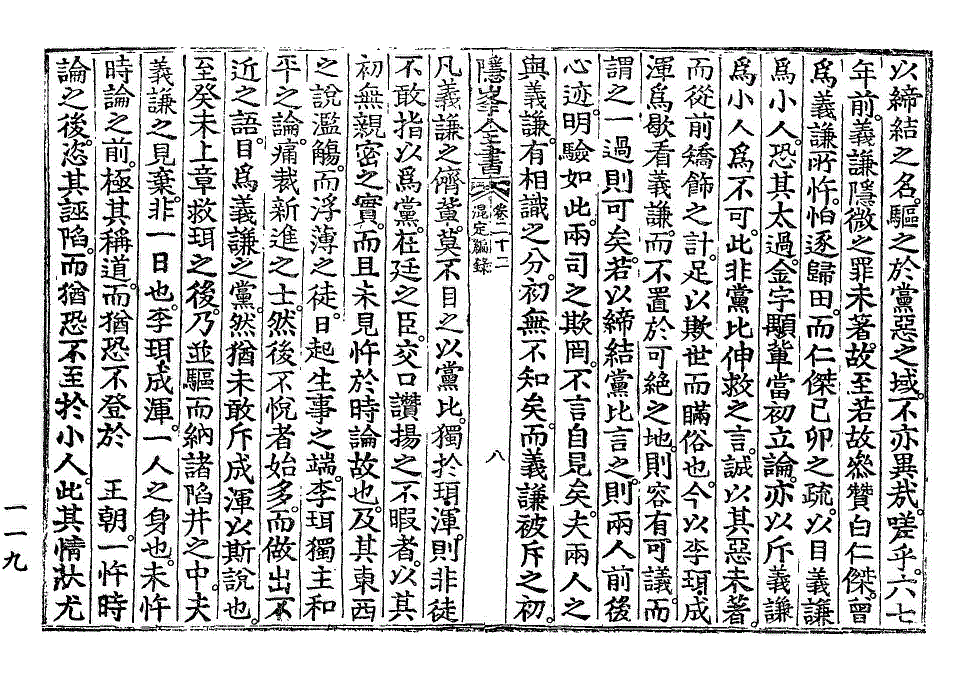 以缔结之名。驱之于党恶之域。不亦异哉。嗟乎。六七年前。义谦隐微之罪未著。故至若故参赞白仁杰。曾为义谦所忤。怕逐归田。而仁杰己卯之疏。以目义谦为小人。恐其太过。金宇颙辈当初立论。亦以斥义谦为小人为不可。此非党比伸救之言。诚以其恶未著。而从前矫饰之计。足以欺世而瞒俗也。今以李珥,成浑为歇看义谦。而不置于可绝之地。则容有可议。而谓之一过则可矣。若以缔结党比言之。则两人前后心迹。明验如此。两司之欺罔。不言自见矣。夫两人之与义谦。有相识之分。初无不知矣。而义谦被斥之初。凡义谦之侪辈。莫不目之以党比。独于珥,浑。则非徒不敢指以为党。在廷之臣。交口赞扬之不暇者。以其初无亲密之实。而且未见忤于时论故也。及其东西之说滥觞。而浮薄之徒。日起生事之端。李珥独主和平之论。痛裁新进之士。然后不悦者始多。而做出不近之语。目为义谦之党。然犹未敢斥成浑以斯说也。至癸未上章救珥之后。乃并驱而纳诸陷井之中。夫义谦之见弃。非一日也。李珥,成浑。一人之身也。未忤时论之前。极其称道。而犹恐不登于 王朝。一忤时论之后。恣其诬陷。而犹恐不至于小人。此其情状尤
以缔结之名。驱之于党恶之域。不亦异哉。嗟乎。六七年前。义谦隐微之罪未著。故至若故参赞白仁杰。曾为义谦所忤。怕逐归田。而仁杰己卯之疏。以目义谦为小人。恐其太过。金宇颙辈当初立论。亦以斥义谦为小人为不可。此非党比伸救之言。诚以其恶未著。而从前矫饰之计。足以欺世而瞒俗也。今以李珥,成浑为歇看义谦。而不置于可绝之地。则容有可议。而谓之一过则可矣。若以缔结党比言之。则两人前后心迹。明验如此。两司之欺罔。不言自见矣。夫两人之与义谦。有相识之分。初无不知矣。而义谦被斥之初。凡义谦之侪辈。莫不目之以党比。独于珥,浑。则非徒不敢指以为党。在廷之臣。交口赞扬之不暇者。以其初无亲密之实。而且未见忤于时论故也。及其东西之说滥觞。而浮薄之徒。日起生事之端。李珥独主和平之论。痛裁新进之士。然后不悦者始多。而做出不近之语。目为义谦之党。然犹未敢斥成浑以斯说也。至癸未上章救珥之后。乃并驱而纳诸陷井之中。夫义谦之见弃。非一日也。李珥,成浑。一人之身也。未忤时论之前。极其称道。而犹恐不登于 王朝。一忤时论之后。恣其诬陷。而犹恐不至于小人。此其情状尤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第 1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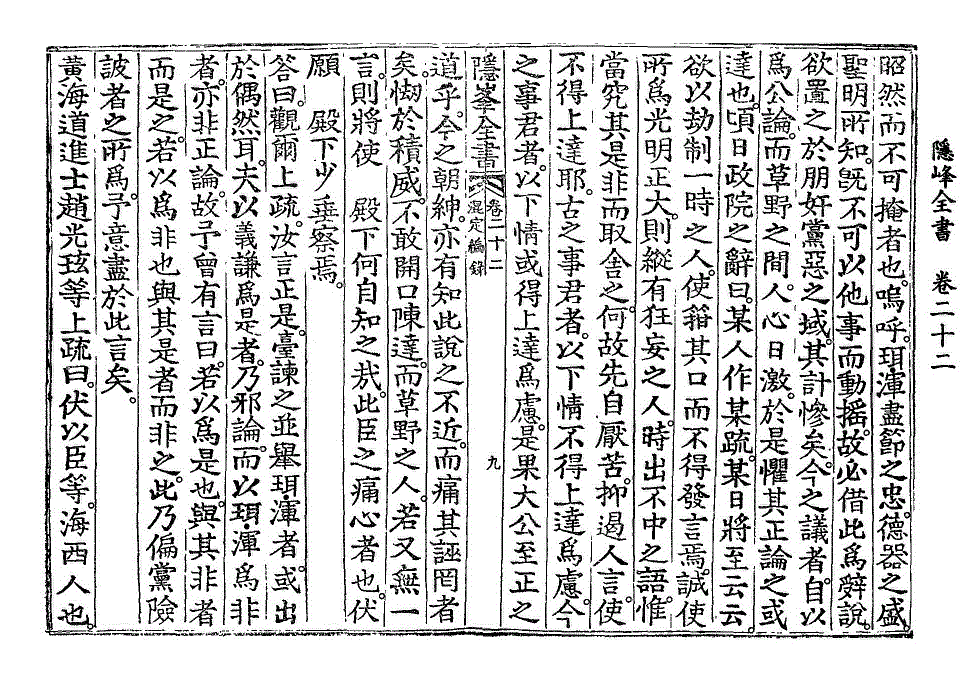 昭然而不可掩者也。呜呼。珥,浑尽节之忠。德器之盛。圣明所知。既不可以他事而动摇。故必借此为辞说。欲置之于朋奸党恶之域。其计惨矣。今之议者。自以为公论。而草野之间。人心日激。于是惧其正论之或达也。顷日政院之辞曰。某人作某疏。某日将至云云。欲以劫制一时之人。使钳其口而不得发言焉。诚使所为光明正大。则纵有狂妄之人。时出不中之语。惟当究其是非而取舍之。何故先自厌苦。抑遏人言。使不得上达耶。古之事君者。以下情不得上达为虑。今之事君者。以下情或得上达为虑。是果大公至正之道乎。今之朝绅。亦有知此说之不近。而痛其诬罔者矣。怯于积威。不敢开口陈达。而草野之人。若又无一言。则将使 殿下何自知之哉。此臣之痛心者也。伏愿 殿下少垂察焉。
昭然而不可掩者也。呜呼。珥,浑尽节之忠。德器之盛。圣明所知。既不可以他事而动摇。故必借此为辞说。欲置之于朋奸党恶之域。其计惨矣。今之议者。自以为公论。而草野之间。人心日激。于是惧其正论之或达也。顷日政院之辞曰。某人作某疏。某日将至云云。欲以劫制一时之人。使钳其口而不得发言焉。诚使所为光明正大。则纵有狂妄之人。时出不中之语。惟当究其是非而取舍之。何故先自厌苦。抑遏人言。使不得上达耶。古之事君者。以下情不得上达为虑。今之事君者。以下情或得上达为虑。是果大公至正之道乎。今之朝绅。亦有知此说之不近。而痛其诬罔者矣。怯于积威。不敢开口陈达。而草野之人。若又无一言。则将使 殿下何自知之哉。此臣之痛心者也。伏愿 殿下少垂察焉。答曰。观尔上疏。汝言正是。台谏之并举珥,浑者。或出于偶然耳。夫以义谦为是者。乃邪论。而以珥,浑为非者。亦非正论。故予曾有言曰。若以为是也。与其非者而是之。若以为非也与其是者而非之。此乃偏党险诐者之所为。予意尽于此言矣。
黄海道进士赵光玹等上疏曰。伏以臣等。海西人也。
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第 1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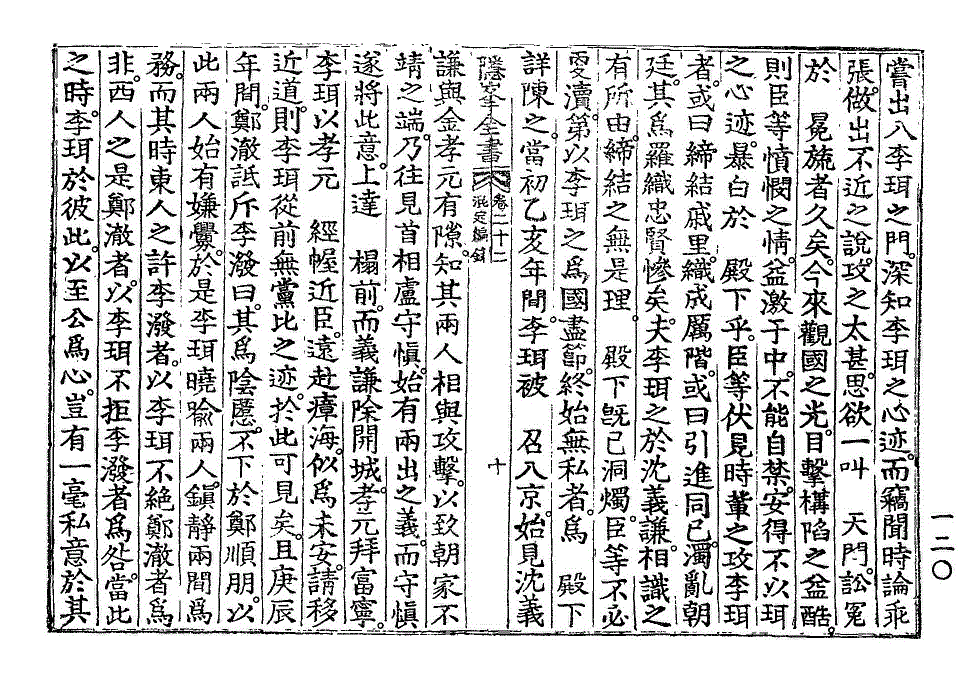 尝出入李珥之门。深知李珥之心迹。而窃闻时论乖张。做出不近之说。攻之太甚。思欲一叫 天门。讼冤于 冕旒者久矣。今来观国之光。目击构陷之益酷。则臣等愤悯之情。益激于中。不能自禁。安得不以珥之心迹。暴白于 殿下乎。臣等伏见时辈之攻李珥者。或曰缔结戚里。织成厉阶。或曰引进同己。浊乱朝廷。其为罗织忠贤惨矣。夫李珥之于沈义谦。相识之有所由。缔结之无是理。 殿下既已洞烛。臣等不必更渎。第以李珥之为国尽节。终始无私者。为 殿下详陈之。当初乙亥年间。李珥被 召入京。始见沈义谦与金孝元有隙。知其两人相与攻击。以致朝家不靖之端。乃往见首相卢守慎。始有两出之义。而守慎遂将此意。上达 榻前。而义谦除开城。孝元拜富宁。李珥以孝元 经幄近臣。远赴瘴海。似为未安。请移近道。则李珥从前无党比之迹。于此可见矣。且庚辰年间。郑澈诋斥李泼曰。其为阴慝。不下于郑顺朋。以此两人始有嫌衅。于是李珥晓喻两人。镇静两间为务。而其时东人之许李泼者。以李珥不绝郑澈者为非。西人之是郑澈者。以李珥不拒李泼者为咎。当此之时。李珥于彼此。以至公为心。岂有一毫私意于其
尝出入李珥之门。深知李珥之心迹。而窃闻时论乖张。做出不近之说。攻之太甚。思欲一叫 天门。讼冤于 冕旒者久矣。今来观国之光。目击构陷之益酷。则臣等愤悯之情。益激于中。不能自禁。安得不以珥之心迹。暴白于 殿下乎。臣等伏见时辈之攻李珥者。或曰缔结戚里。织成厉阶。或曰引进同己。浊乱朝廷。其为罗织忠贤惨矣。夫李珥之于沈义谦。相识之有所由。缔结之无是理。 殿下既已洞烛。臣等不必更渎。第以李珥之为国尽节。终始无私者。为 殿下详陈之。当初乙亥年间。李珥被 召入京。始见沈义谦与金孝元有隙。知其两人相与攻击。以致朝家不靖之端。乃往见首相卢守慎。始有两出之义。而守慎遂将此意。上达 榻前。而义谦除开城。孝元拜富宁。李珥以孝元 经幄近臣。远赴瘴海。似为未安。请移近道。则李珥从前无党比之迹。于此可见矣。且庚辰年间。郑澈诋斥李泼曰。其为阴慝。不下于郑顺朋。以此两人始有嫌衅。于是李珥晓喻两人。镇静两间为务。而其时东人之许李泼者。以李珥不绝郑澈者为非。西人之是郑澈者。以李珥不拒李泼者为咎。当此之时。李珥于彼此。以至公为心。岂有一毫私意于其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第 1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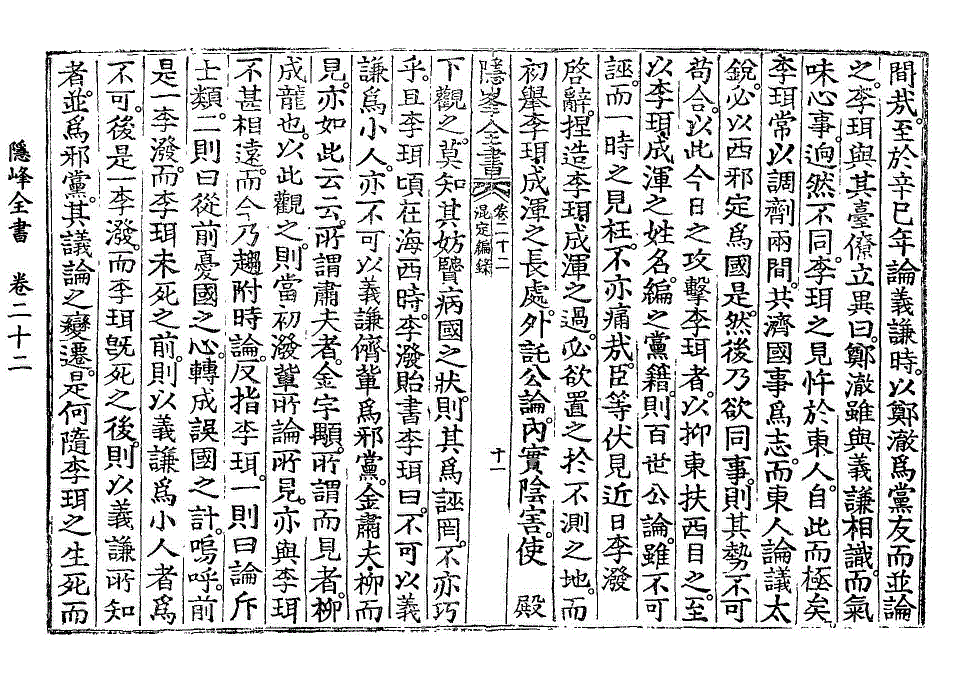 间哉。至于辛巳年论义谦时。以郑澈为党友而并论之。李珥与其台僚立异曰。郑澈虽与义谦相识。而气味心事。迥然不同。李珥之见忤于东人。自此而极矣。李珥常以调剂两间。共济国事为志。而东人论议太锐。必以西邪定为国是。然后乃欲同事。则其势不可苟合。以此今日之攻击李珥者。以抑东扶西目之。至以李珥,成浑之姓名。编之党籍。则百世公论。虽不可诬。而一时之见枉。不亦痛哉。臣等伏见近日李泼 启辞。捏造李珥,成浑之过。必欲置之于不测之地。而初举李珥,成浑之长处。外托公论。内实阴害。使 殿下观之。莫知其妨贤病国之状。则其为诬罔。不亦巧乎。且李珥顷在海西时。李泼贻书李珥曰。不可以义谦为小人。亦不可以义谦侪辈为邪党。金肃夫,柳而见。亦如此云云。所谓肃夫者。金宇颙。所谓而见者。柳成龙也。以此观之。则当初泼辈所论所见。亦与李珥不甚相远。而今乃趋附时论。反指李珥。一则曰论斥士类。二则曰从前忧国之心。转成误国之计。呜呼。前是一李泼。而李珥未死之前。则以义谦为小人者为不可。后是一李泼。而李珥既死之后。则以义谦所知者。并为邪党。其议论之变迁。是何随李珥之生死而
间哉。至于辛巳年论义谦时。以郑澈为党友而并论之。李珥与其台僚立异曰。郑澈虽与义谦相识。而气味心事。迥然不同。李珥之见忤于东人。自此而极矣。李珥常以调剂两间。共济国事为志。而东人论议太锐。必以西邪定为国是。然后乃欲同事。则其势不可苟合。以此今日之攻击李珥者。以抑东扶西目之。至以李珥,成浑之姓名。编之党籍。则百世公论。虽不可诬。而一时之见枉。不亦痛哉。臣等伏见近日李泼 启辞。捏造李珥,成浑之过。必欲置之于不测之地。而初举李珥,成浑之长处。外托公论。内实阴害。使 殿下观之。莫知其妨贤病国之状。则其为诬罔。不亦巧乎。且李珥顷在海西时。李泼贻书李珥曰。不可以义谦为小人。亦不可以义谦侪辈为邪党。金肃夫,柳而见。亦如此云云。所谓肃夫者。金宇颙。所谓而见者。柳成龙也。以此观之。则当初泼辈所论所见。亦与李珥不甚相远。而今乃趋附时论。反指李珥。一则曰论斥士类。二则曰从前忧国之心。转成误国之计。呜呼。前是一李泼。而李珥未死之前。则以义谦为小人者为不可。后是一李泼。而李珥既死之后。则以义谦所知者。并为邪党。其议论之变迁。是何随李珥之生死而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第 1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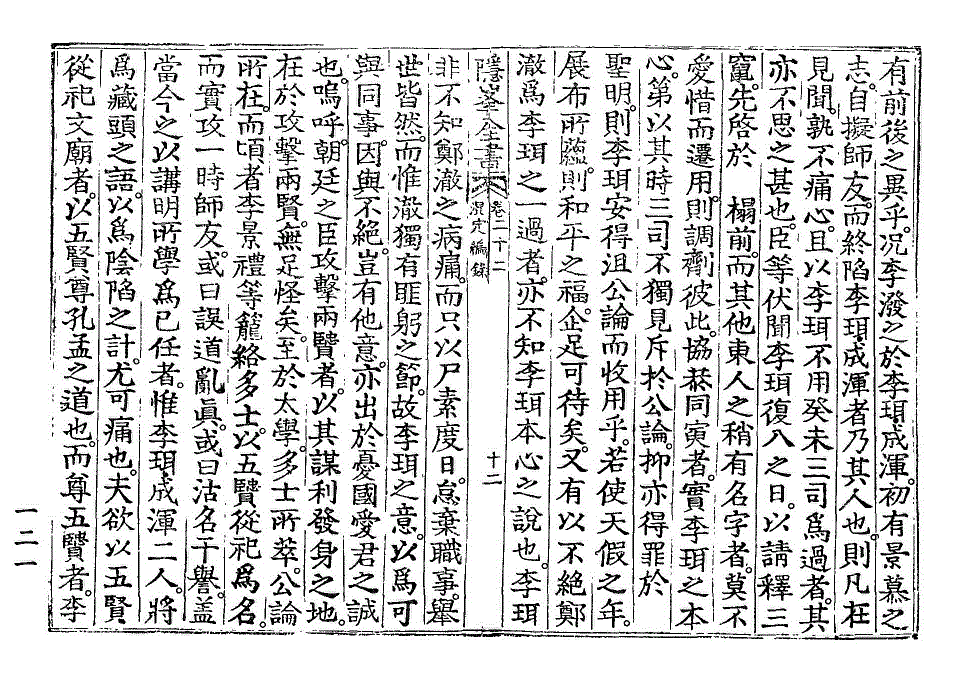 有前后之异乎。况李泼之于李珥,成浑。初有景慕之志。自拟师友。而终陷李珥,成浑者乃其人也。则凡在见闻。孰不痛心。且以李珥不用癸未三司为过者。其亦不思之甚也。臣等伏闻李珥复入之日。以请释三窜。先启于 榻前。而其他东人之稍有名字者。莫不爱惜而迁用。则调剂彼此。协恭同寅者。实李珥之本心。第以其时三司不独见斥于公论。抑亦得罪于 圣明。则李珥安得沮公论而收用乎。若使天假之年。展布所蕴。则和平之福。企足可待矣。又有以不绝郑澈为李珥之一过者。亦不知李珥本心之说也。李珥非不知郑澈之病痛。而只以尸素度日。怠弃职事。举世皆然。而惟澈独有匪躬之节。故李珥之意。以为可与同事。因与不绝。岂有他意。亦出于忧国爱君之诚也。呜呼。朝廷之臣攻击两贤者。以其谋利发身之地。在于攻击两贤。无足怪矣。至于太学。多士所萃。公论所在。而顷者李景礼等笼络多士。以五贤从祀为名。而实攻一时师友。或曰误道乱真。或曰沽名干誉。盖当今之以讲明所学为己任者。惟李珥,成浑二人。将为藏头之语。以为阴陷之计。尤可痛也。夫欲以五贤从祀文庙者。以五贤尊孔孟之道也。而尊五贤者。李
有前后之异乎。况李泼之于李珥,成浑。初有景慕之志。自拟师友。而终陷李珥,成浑者乃其人也。则凡在见闻。孰不痛心。且以李珥不用癸未三司为过者。其亦不思之甚也。臣等伏闻李珥复入之日。以请释三窜。先启于 榻前。而其他东人之稍有名字者。莫不爱惜而迁用。则调剂彼此。协恭同寅者。实李珥之本心。第以其时三司不独见斥于公论。抑亦得罪于 圣明。则李珥安得沮公论而收用乎。若使天假之年。展布所蕴。则和平之福。企足可待矣。又有以不绝郑澈为李珥之一过者。亦不知李珥本心之说也。李珥非不知郑澈之病痛。而只以尸素度日。怠弃职事。举世皆然。而惟澈独有匪躬之节。故李珥之意。以为可与同事。因与不绝。岂有他意。亦出于忧国爱君之诚也。呜呼。朝廷之臣攻击两贤者。以其谋利发身之地。在于攻击两贤。无足怪矣。至于太学。多士所萃。公论所在。而顷者李景礼等笼络多士。以五贤从祀为名。而实攻一时师友。或曰误道乱真。或曰沽名干誉。盖当今之以讲明所学为己任者。惟李珥,成浑二人。将为藏头之语。以为阴陷之计。尤可痛也。夫欲以五贤从祀文庙者。以五贤尊孔孟之道也。而尊五贤者。李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第 1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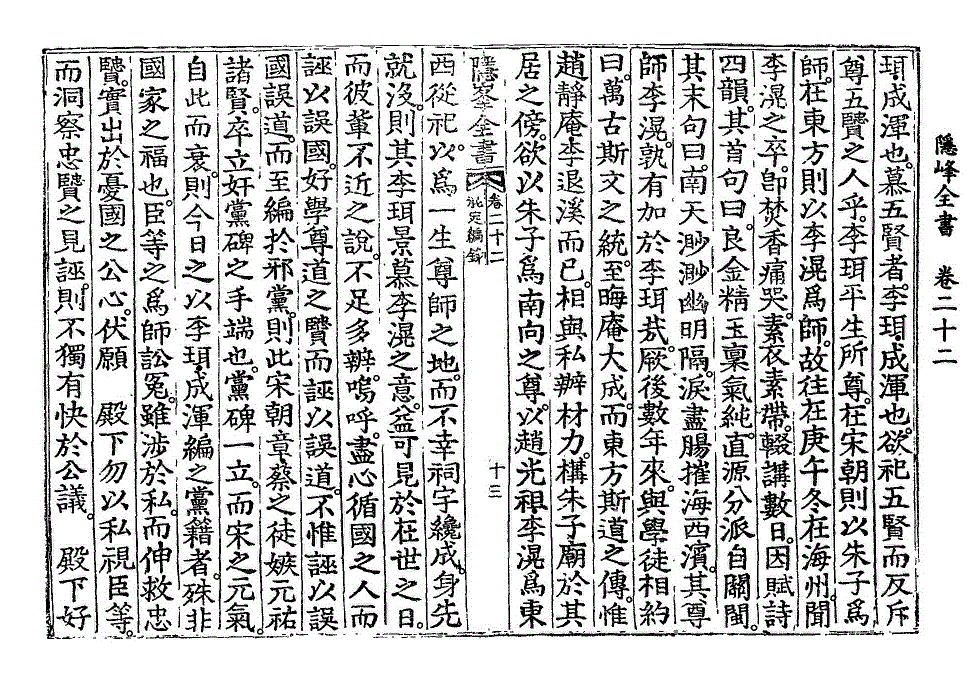 珥,成浑也。慕五贤者。李珥,成浑也。欲祀五贤而反斥尊五贤之人乎。李珥平生所尊。在宋朝则以朱子为师。在东方则以李滉为师。故往在庚午冬在海州。闻李滉之卒。即焚香痛哭。素衣素带。辍讲数日。因赋诗四韵。其首句曰。良金精玉禀气纯。直源分派自关闽。其末句曰。南天渺渺幽明隔。泪尽肠摧海西滨。其尊师李滉。孰有加于李珥哉。厥后数年来。与学徒相约曰。万古斯交之统。至晦庵大成。而东方斯道之传。惟赵静庵,李退溪而已。相与私办材力。构朱子庙于其居之傍。欲以朱子为南向之尊。以赵光祖,李滉为东西从祀。以为一生尊师之地。而不幸祠宇才成。身先就没。则其李珥景慕李滉之意。益可见于在世之日。而彼辈不近之说。不足多辨。呜呼。尽心循国之人而诬以误国。好学尊道之贤而诬以误道。不惟诬以误国误道。而至编于邪党。则此宋朝章,蔡之徒嫉元祐诸贤。卒立奸党碑之手端也。党碑一立。而宋之元气。自此而衰。则今日之以李珥,成浑编之党籍者。殊非国家之福也。臣等之为师讼冤。虽涉于私。而伸救忠贤。实出于忧国之公心。伏愿 殿下勿以私视臣等。而洞察忠贤之见诬。则不独有快于公议。 殿下好
珥,成浑也。慕五贤者。李珥,成浑也。欲祀五贤而反斥尊五贤之人乎。李珥平生所尊。在宋朝则以朱子为师。在东方则以李滉为师。故往在庚午冬在海州。闻李滉之卒。即焚香痛哭。素衣素带。辍讲数日。因赋诗四韵。其首句曰。良金精玉禀气纯。直源分派自关闽。其末句曰。南天渺渺幽明隔。泪尽肠摧海西滨。其尊师李滉。孰有加于李珥哉。厥后数年来。与学徒相约曰。万古斯交之统。至晦庵大成。而东方斯道之传。惟赵静庵,李退溪而已。相与私办材力。构朱子庙于其居之傍。欲以朱子为南向之尊。以赵光祖,李滉为东西从祀。以为一生尊师之地。而不幸祠宇才成。身先就没。则其李珥景慕李滉之意。益可见于在世之日。而彼辈不近之说。不足多辨。呜呼。尽心循国之人而诬以误国。好学尊道之贤而诬以误道。不惟诬以误国误道。而至编于邪党。则此宋朝章,蔡之徒嫉元祐诸贤。卒立奸党碑之手端也。党碑一立。而宋之元气。自此而衰。则今日之以李珥,成浑编之党籍者。殊非国家之福也。臣等之为师讼冤。虽涉于私。而伸救忠贤。实出于忧国之公心。伏愿 殿下勿以私视臣等。而洞察忠贤之见诬。则不独有快于公议。 殿下好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第 1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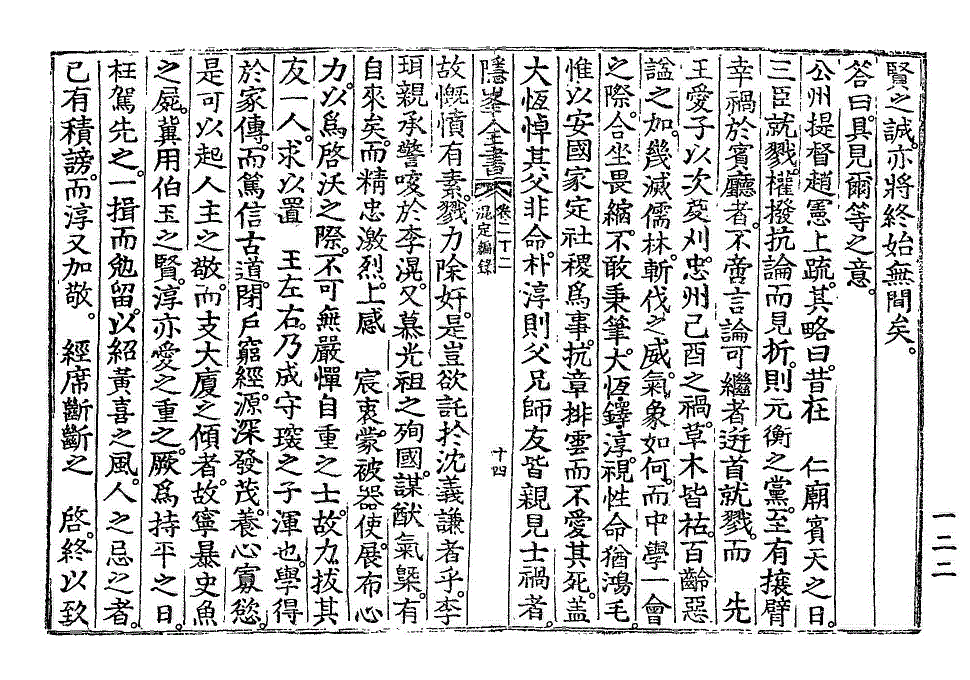 贤之诚。亦将终始无间矣。
贤之诚。亦将终始无间矣。答曰。具见尔等之意。
公州提督赵宪上疏。其略曰。昔在 仁庙宾天之日。三臣就戮。权拨抗论而见折。则元衡之党。至有攘臂幸祸于宾厅者。不啻言论可继者迸首就戮。而 先王爱子以次芟刈。忠州己酉之祸。草木皆枯。百龄恶谥之加。几灭儒林。斩伐之威。气象如何。而中学一会之际。合坐畏缩。不敢秉笔。大恒,铎,淳。视性命犹鸿毛。惟以安国家定社稷为事。抗章排云而不爱其死。盖大恒悼其父非命。朴淳则父兄师友皆亲见士祸者。故慨愤有素。戮力除奸。是岂欲托于沈义谦者乎。李珥亲承警咳于李滉。又慕光祖之殉国。谋猷气槩。有自来矣。而精忠激烈。上感 宸衷。蒙被器使。展布心力。以为启沃之际。不可无严惮自重之士。故力拔其友一人。求以置 王左右。乃成守琛之子浑也。学得于家传。而笃信古道。闭户穷经。源深发茂。养心寡欲。是可以起人主之敬。而支大厦之倾者。故宁暴史鱼之尸。冀用伯玉之贤。淳亦爱之重之。厥为持平之日。枉驾先之。一揖而勉留。以绍黄喜之风。人之忌之者。已有积谤。而淳又加敬。 经席断断之 启。终以致
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第 1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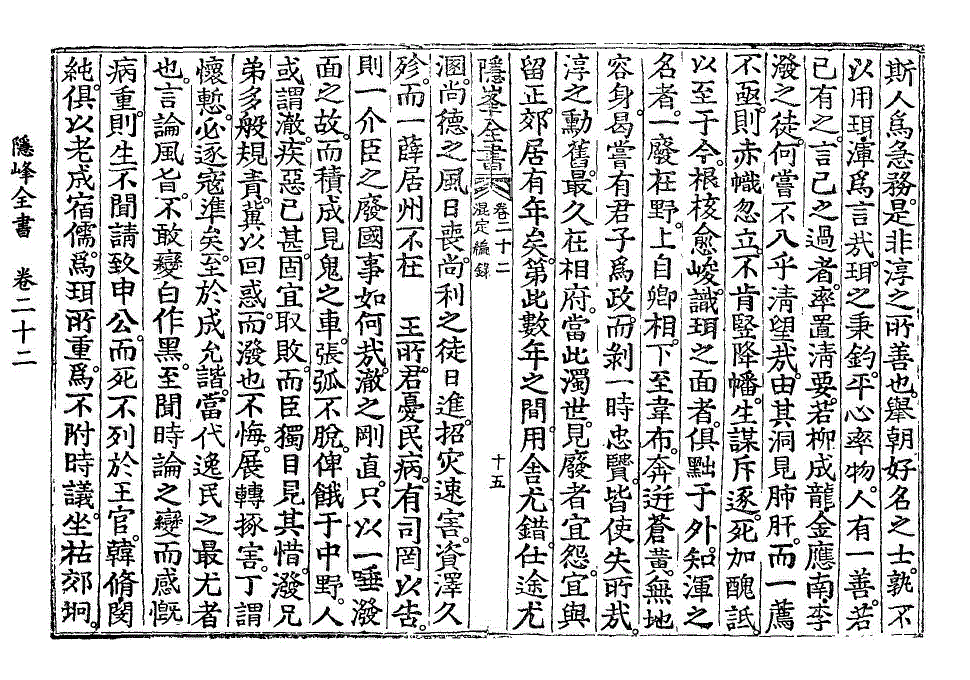 斯人为急务。是非淳之所善也。举朝好名之士。孰不以用珥,浑为言哉。珥之秉钓。平心率物。人有一善。若已有之。言己之过者。率置清要。若柳成龙,金应南,李泼之徒。何尝不入乎清望哉。由其洞见肺肝。而一荐不亟。则赤帜忽立不肯竖降幡。生谋斥逐。死加丑诋。以至于今。根核愈峻。识珥之面者。俱黜于外。知浑之名者。一废在野。上自卿相。下至韦布。奔迸苍黄。无地容身。曷尝有君子为政。而剥一时忠贤。皆使失所哉。淳之勋旧。最久在相府。当此浊世。见废者宜怨。宜与留正。郊居有年矣。第此数年之间。用舍尤错。仕途尤溷尚德之风日丧。尚利之徒日进。招灾速害。资泽久殄。而一薛居州不在 王所。君忧民病。有司罔以告。则一介臣之废国事如何哉。澈之刚直。只以一唾泼面之故。而积成见鬼之车。张弧不脱。俾饿于中野。人或谓澈。疾恶已甚。固宜取败。而臣独目见其惜。泼兄弟多般规责。冀以回惑。而泼也不悔。展转椓害。丁谓怀惭。必逐寇准矣。至于成允谐。当代逸民之最尤者也。言论风旨。不敢变白作黑。至闻时论之变而感慨病重。则生不闻请致申公。而死不列于王官。韩脩,闵纯。俱以老成宿儒。为珥所重。为不附时议。坐枯郊坰。
斯人为急务。是非淳之所善也。举朝好名之士。孰不以用珥,浑为言哉。珥之秉钓。平心率物。人有一善。若已有之。言己之过者。率置清要。若柳成龙,金应南,李泼之徒。何尝不入乎清望哉。由其洞见肺肝。而一荐不亟。则赤帜忽立不肯竖降幡。生谋斥逐。死加丑诋。以至于今。根核愈峻。识珥之面者。俱黜于外。知浑之名者。一废在野。上自卿相。下至韦布。奔迸苍黄。无地容身。曷尝有君子为政。而剥一时忠贤。皆使失所哉。淳之勋旧。最久在相府。当此浊世。见废者宜怨。宜与留正。郊居有年矣。第此数年之间。用舍尤错。仕途尤溷尚德之风日丧。尚利之徒日进。招灾速害。资泽久殄。而一薛居州不在 王所。君忧民病。有司罔以告。则一介臣之废国事如何哉。澈之刚直。只以一唾泼面之故。而积成见鬼之车。张弧不脱。俾饿于中野。人或谓澈。疾恶已甚。固宜取败。而臣独目见其惜。泼兄弟多般规责。冀以回惑。而泼也不悔。展转椓害。丁谓怀惭。必逐寇准矣。至于成允谐。当代逸民之最尤者也。言论风旨。不敢变白作黑。至闻时论之变而感慨病重。则生不闻请致申公。而死不列于王官。韩脩,闵纯。俱以老成宿儒。为珥所重。为不附时议。坐枯郊坰。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第 1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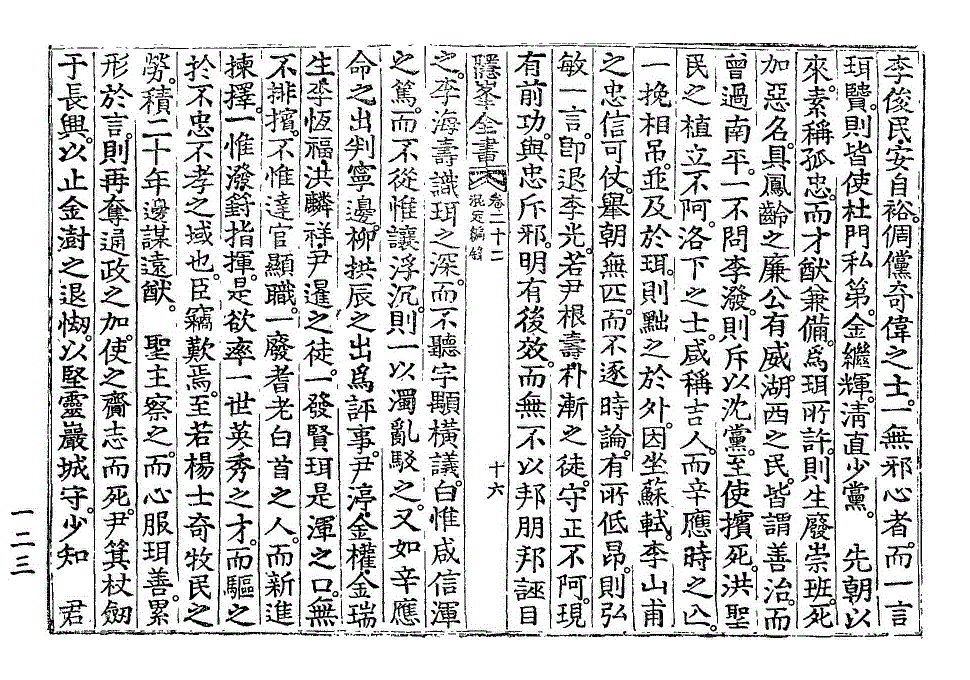 李俊民,安自裕。倜傥奇伟之士。一无邪心者。而一言珥贤。则皆使杜门私第。金继辉。清直少党。 先朝以来。素称孤忠。而才猷兼备。为珥所许。则生废崇班。死加恶名。具凤龄之廉公有威。湖西之民。皆谓善治。而曾过南平。一不问李泼。则斥以沈党。至使摈死。洪圣民之植立不阿。洛下之士。咸称吉人。而辛应时之亡。一挽相吊。并及于珥。则黜之于外。因坐苏轼。李山甫之忠信可仗。举朝无匹。而不逐时论。有所低昂。则弘敏一言。即退李光。若尹根寿,朴渐之徒。守正不阿。现有前功。与忠斥邪。明有后效。而无不以邦朋邦诬目之。李海寿识珥之深。而不听宇颙横议。白惟咸信浑之笃。而不从惟让浮沈。则一以浊乱驳之。又如辛应命之出判宁边。柳拱辰之出为评事。尹渟,金权,金瑞生,李恒福,洪麟祥,尹暹之徒。一发贤珥是浑之口。无不排摈。不惟达官显职。一废耆老白首之人。而新进拣择。一惟泼,篈指挥。是欲率一世英秀之才。而驱之于不忠不孝之域也。臣窃叹焉。至若杨士奇牧民之劳。积二十年边谋远猷。 圣主察之。而心服珥善。累形于言。则再夺通政之加。使之赍志而死。尹箕杖剑于长兴。以止金澍之退怯。以坚灵岩城守。少知 君
李俊民,安自裕。倜傥奇伟之士。一无邪心者。而一言珥贤。则皆使杜门私第。金继辉。清直少党。 先朝以来。素称孤忠。而才猷兼备。为珥所许。则生废崇班。死加恶名。具凤龄之廉公有威。湖西之民。皆谓善治。而曾过南平。一不问李泼。则斥以沈党。至使摈死。洪圣民之植立不阿。洛下之士。咸称吉人。而辛应时之亡。一挽相吊。并及于珥。则黜之于外。因坐苏轼。李山甫之忠信可仗。举朝无匹。而不逐时论。有所低昂。则弘敏一言。即退李光。若尹根寿,朴渐之徒。守正不阿。现有前功。与忠斥邪。明有后效。而无不以邦朋邦诬目之。李海寿识珥之深。而不听宇颙横议。白惟咸信浑之笃。而不从惟让浮沈。则一以浊乱驳之。又如辛应命之出判宁边。柳拱辰之出为评事。尹渟,金权,金瑞生,李恒福,洪麟祥,尹暹之徒。一发贤珥是浑之口。无不排摈。不惟达官显职。一废耆老白首之人。而新进拣择。一惟泼,篈指挥。是欲率一世英秀之才。而驱之于不忠不孝之域也。臣窃叹焉。至若杨士奇牧民之劳。积二十年边谋远猷。 圣主察之。而心服珥善。累形于言。则再夺通政之加。使之赍志而死。尹箕杖剑于长兴。以止金澍之退怯。以坚灵岩城守。少知 君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第 1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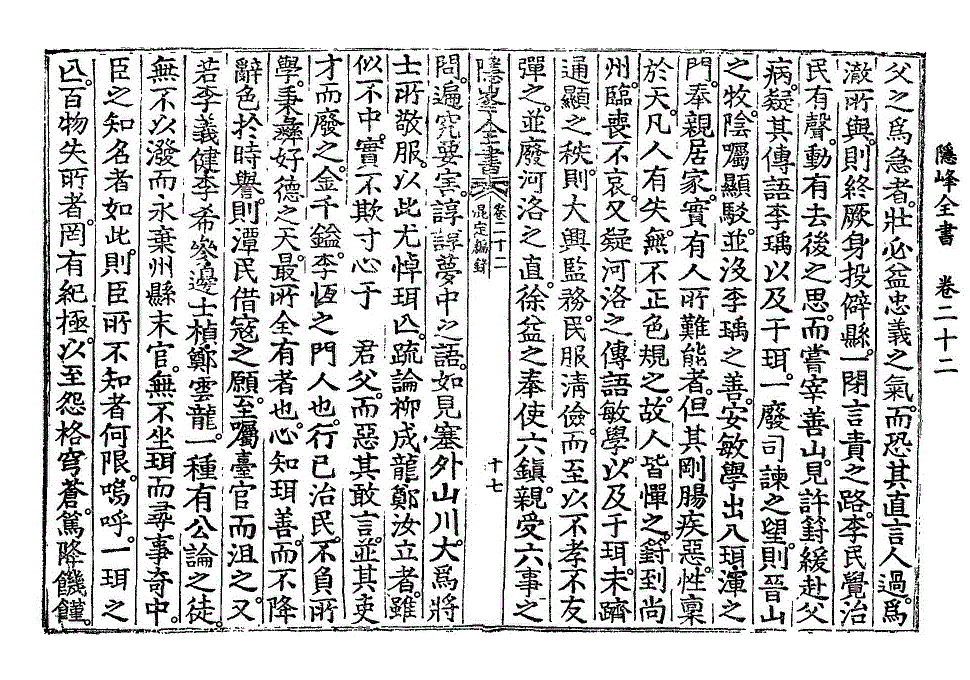 父之为急者。壮必益忠义之气。而恐其直言人过。为澈所与。则终厥身投僻县。一闭言责之路。李民觉治民有声。动有去后之思。而尝宰善山。见许篈缓赴父病。疑其传语李瑀以及于珥。一废司谏之望。则晋山之牧。阴嘱显驳。并没李瑀之善。安敏学出入珥,浑之门。奉亲居家。实有人所难能者。但其刚肠疾恶。性禀于天。凡人有失。无不正色规之。故人皆惮之。篈到尚州。临丧不哀。又疑河洛之传语敏学。以及于珥。未跻通显之秩。则大兴监务。民服清俭。而至以不孝不友弹之。并废河洛之直。徐益之奉使六镇。亲受六事之问。遍究要害。谆谆梦中之语。如见塞外山川。大为将士所敬服。以此尤悼珥亡。疏论柳成龙,郑汝立者。虽似不中。实不欺寸心于 君父。而恶其敢言。并其吏才而废之。金千镒。李恒之门人也。行已治民。不负所学。秉彝好德之天。最所全有者也。心知珥善。而不降辞色于时誉。则潭民借寇之愿。至嘱台官而沮之。又若李义健,李希参,边士桢,郑云龙。一种有公论之徒。无不以泼而永弃州县末官。无不坐珥而寻事奇中。臣之知名者如此。则臣所不知者何限。呜呼。一珥之亡。百物失所者。罔有纪极。以至怨格穹苍。笃降饥馑。
父之为急者。壮必益忠义之气。而恐其直言人过。为澈所与。则终厥身投僻县。一闭言责之路。李民觉治民有声。动有去后之思。而尝宰善山。见许篈缓赴父病。疑其传语李瑀以及于珥。一废司谏之望。则晋山之牧。阴嘱显驳。并没李瑀之善。安敏学出入珥,浑之门。奉亲居家。实有人所难能者。但其刚肠疾恶。性禀于天。凡人有失。无不正色规之。故人皆惮之。篈到尚州。临丧不哀。又疑河洛之传语敏学。以及于珥。未跻通显之秩。则大兴监务。民服清俭。而至以不孝不友弹之。并废河洛之直。徐益之奉使六镇。亲受六事之问。遍究要害。谆谆梦中之语。如见塞外山川。大为将士所敬服。以此尤悼珥亡。疏论柳成龙,郑汝立者。虽似不中。实不欺寸心于 君父。而恶其敢言。并其吏才而废之。金千镒。李恒之门人也。行已治民。不负所学。秉彝好德之天。最所全有者也。心知珥善。而不降辞色于时誉。则潭民借寇之愿。至嘱台官而沮之。又若李义健,李希参,边士桢,郑云龙。一种有公论之徒。无不以泼而永弃州县末官。无不坐珥而寻事奇中。臣之知名者如此。则臣所不知者何限。呜呼。一珥之亡。百物失所者。罔有纪极。以至怨格穹苍。笃降饥馑。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第 1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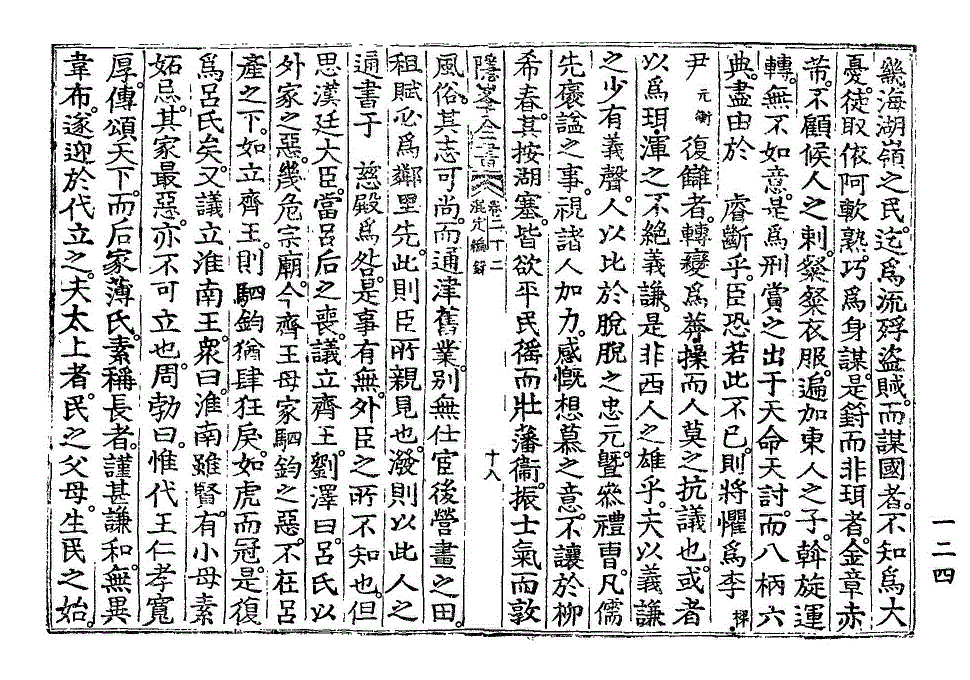 畿海湖岭之民。迄为流殍盗贼。而谋国者。不知为大忧。徒取依阿软熟。巧为身谋。是篈而非珥者。金章赤芾。不顾候人之刺。粲粲衣服。遍加东人之子。斡旋运转。无不如意。是为刑赏之出于天命天讨。而八柄六典。尽由于 睿断乎。臣恐若此不已。则将惧为李(梁),尹(元衡)复雠者。转变为莽,操而人莫之抗议也。或者以为珥,浑之不绝义谦。是非西人之雄乎。夫以义谦之少有义声。人以比于脱脱之忠元。暨参礼曹。凡儒先褒谥之事。视诸人加力。感慨想慕之意。不让于柳希春。其按湖塞。皆欲平民徭而壮藩卫。振士气而敦风俗其志可尚。而通津旧业。别无仕宦后营画之田。租赋必为邻里先。此则臣所亲见也。泼则以此人之通书于 慈殿为咎。是事有无。外臣之所不知也。但思汉廷大臣。当吕后之丧。议立齐王。刘泽曰。吕氏以外家之恶。几危宗庙。今齐王母家驷钧之恶。不在吕产之下。如立齐王。则驷钧犹肆狂戾。如虎而冠。是复为吕氏矣。又议立淮南王。众曰。淮南虽贤。有小母素妒忌。其家最恶。亦不可立也。周勃曰。惟代王仁孝宽厚。传颂天下。而后家薄氏。素称长者。谨甚谦和。无异韦布。遂迎于代立之。夫太上者。民之父母。生民之始。
畿海湖岭之民。迄为流殍盗贼。而谋国者。不知为大忧。徒取依阿软熟。巧为身谋。是篈而非珥者。金章赤芾。不顾候人之刺。粲粲衣服。遍加东人之子。斡旋运转。无不如意。是为刑赏之出于天命天讨。而八柄六典。尽由于 睿断乎。臣恐若此不已。则将惧为李(梁),尹(元衡)复雠者。转变为莽,操而人莫之抗议也。或者以为珥,浑之不绝义谦。是非西人之雄乎。夫以义谦之少有义声。人以比于脱脱之忠元。暨参礼曹。凡儒先褒谥之事。视诸人加力。感慨想慕之意。不让于柳希春。其按湖塞。皆欲平民徭而壮藩卫。振士气而敦风俗其志可尚。而通津旧业。别无仕宦后营画之田。租赋必为邻里先。此则臣所亲见也。泼则以此人之通书于 慈殿为咎。是事有无。外臣之所不知也。但思汉廷大臣。当吕后之丧。议立齐王。刘泽曰。吕氏以外家之恶。几危宗庙。今齐王母家驷钧之恶。不在吕产之下。如立齐王。则驷钧犹肆狂戾。如虎而冠。是复为吕氏矣。又议立淮南王。众曰。淮南虽贤。有小母素妒忌。其家最恶。亦不可立也。周勃曰。惟代王仁孝宽厚。传颂天下。而后家薄氏。素称长者。谨甚谦和。无异韦布。遂迎于代立之。夫太上者。民之父母。生民之始。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第 1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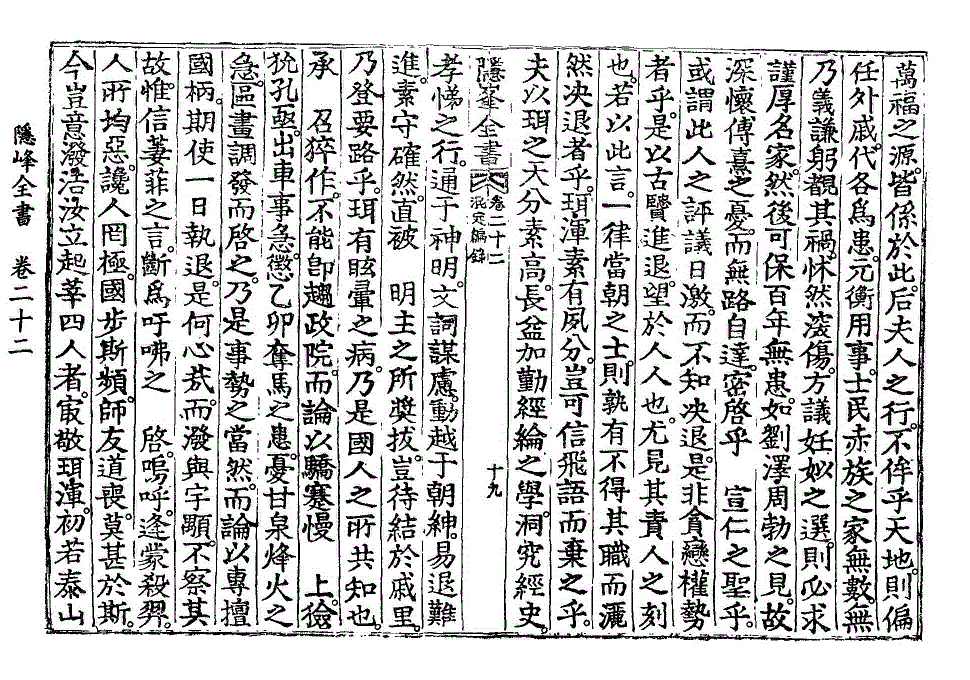 万福之源。皆系于此。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偏任外戚。代各为患。元衡用事。士民赤族之家无数。无乃义谦躬睹其祸。怵然深伤。方议妊姒之选。则必求谨厚名家。然后可保百年无患。如刘泽,周勃之见。故深怀传熹之忧。而无路自达。密启乎 宣仁之圣乎。或谓此人之评议日激。而不知决退。是非贪恋权势者乎。是以古贤进退。望于人人也。尤见其责人之刻也。若以此言。一律当朝之士。则孰有不得其职而洒然决退者乎。珥,浑素有夙分。岂可信飞语而弃之乎。夫以珥之天分素高。长益加勤经纶之学。洞究经史。孝悌之行。通于神明。文词谋虑。动越于朝绅。易退难进。素守确然。直被 明主之所奖拔。岂待结于戚里。乃登要路乎。珥有眩晕之病。乃是国人之所共知也。承 召猝作。不能即趋政院。而论以骄蹇慢 上。猃狁孔亟。出车事急。惩乙卯夺马之患。忧甘泉烽火之急。区画调发而启之。乃是事势之当然。而论以专擅国柄。期使一日执退。是何心哉。而泼与宇颙。不察其故。惟信萋菲之言。断为吁咈之 启。呜呼。逢蒙杀羿。人所均恶。谗人罔极。国步斯频。师友道丧。莫甚于斯。今岂意泼,洁,汝立起莘四人者。最敬珥,浑。初若泰山
万福之源。皆系于此。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偏任外戚。代各为患。元衡用事。士民赤族之家无数。无乃义谦躬睹其祸。怵然深伤。方议妊姒之选。则必求谨厚名家。然后可保百年无患。如刘泽,周勃之见。故深怀传熹之忧。而无路自达。密启乎 宣仁之圣乎。或谓此人之评议日激。而不知决退。是非贪恋权势者乎。是以古贤进退。望于人人也。尤见其责人之刻也。若以此言。一律当朝之士。则孰有不得其职而洒然决退者乎。珥,浑素有夙分。岂可信飞语而弃之乎。夫以珥之天分素高。长益加勤经纶之学。洞究经史。孝悌之行。通于神明。文词谋虑。动越于朝绅。易退难进。素守确然。直被 明主之所奖拔。岂待结于戚里。乃登要路乎。珥有眩晕之病。乃是国人之所共知也。承 召猝作。不能即趋政院。而论以骄蹇慢 上。猃狁孔亟。出车事急。惩乙卯夺马之患。忧甘泉烽火之急。区画调发而启之。乃是事势之当然。而论以专擅国柄。期使一日执退。是何心哉。而泼与宇颙。不察其故。惟信萋菲之言。断为吁咈之 启。呜呼。逢蒙杀羿。人所均恶。谗人罔极。国步斯频。师友道丧。莫甚于斯。今岂意泼,洁,汝立起莘四人者。最敬珥,浑。初若泰山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第 125L 页
 北斗。至于朝夕参候。而一荐不亟。反若豺虎毒药。起莘则日毁于卿相之门。又与金昌一迭下岭南。遍间于名流。必务去之。然后快于其心。自古以来。曷尝有害师反道而能爱其君者乎。臣与宇颙。为同年出身。而同为中学典籍。汝立其时训导也。喜其同登珥,浑之门。拣诲儒生之约甫定而迁官。自此而后。尝拟为善人。又与泼,洁交契尤甚者。只为笃信珥,浑而已。及夫浮议峥嵘。崔永庆朝过而詈珥。金宇颙夕至而嘲珥。臣始疑之。谓永庆林下无求之人。而宇颙进退端方之士也。其所讥呵。必有所自。及乎三司交攻。天枢震摇。河洛谠论。久稽于政院。成浑直言。人指为私护。许篈椓贤之疏。则世不怪其欺罔 君父。乃知细人情状。绸缪纠结。必欲使冰为炭而指鹿为马。傥非 天日之明。旁烛魍魉。则南衮所为。必出于此辈。而鱼肉忠贤。世不之惜矣。臣于是䀌然伤心。抵书于李泼。俾于居忧栾棘。心无外慕之日。深惟遂初之是。而再思朋亡之戒。泼有答书曰。何不观于柳襄阳之远贬乎。宇颙时按湖南。其往复之书。亦以梦鹤外注为咎。臣则素知梦鹤之为不忠也。梦鹤之为台谏也。欲论尹毅中贪邪之状。泼也与梦鹤交厚。往言梦鹤。为停
北斗。至于朝夕参候。而一荐不亟。反若豺虎毒药。起莘则日毁于卿相之门。又与金昌一迭下岭南。遍间于名流。必务去之。然后快于其心。自古以来。曷尝有害师反道而能爱其君者乎。臣与宇颙。为同年出身。而同为中学典籍。汝立其时训导也。喜其同登珥,浑之门。拣诲儒生之约甫定而迁官。自此而后。尝拟为善人。又与泼,洁交契尤甚者。只为笃信珥,浑而已。及夫浮议峥嵘。崔永庆朝过而詈珥。金宇颙夕至而嘲珥。臣始疑之。谓永庆林下无求之人。而宇颙进退端方之士也。其所讥呵。必有所自。及乎三司交攻。天枢震摇。河洛谠论。久稽于政院。成浑直言。人指为私护。许篈椓贤之疏。则世不怪其欺罔 君父。乃知细人情状。绸缪纠结。必欲使冰为炭而指鹿为马。傥非 天日之明。旁烛魍魉。则南衮所为。必出于此辈。而鱼肉忠贤。世不之惜矣。臣于是䀌然伤心。抵书于李泼。俾于居忧栾棘。心无外慕之日。深惟遂初之是。而再思朋亡之戒。泼有答书曰。何不观于柳襄阳之远贬乎。宇颙时按湖南。其往复之书。亦以梦鹤外注为咎。臣则素知梦鹤之为不忠也。梦鹤之为台谏也。欲论尹毅中贪邪之状。泼也与梦鹤交厚。往言梦鹤。为停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第 1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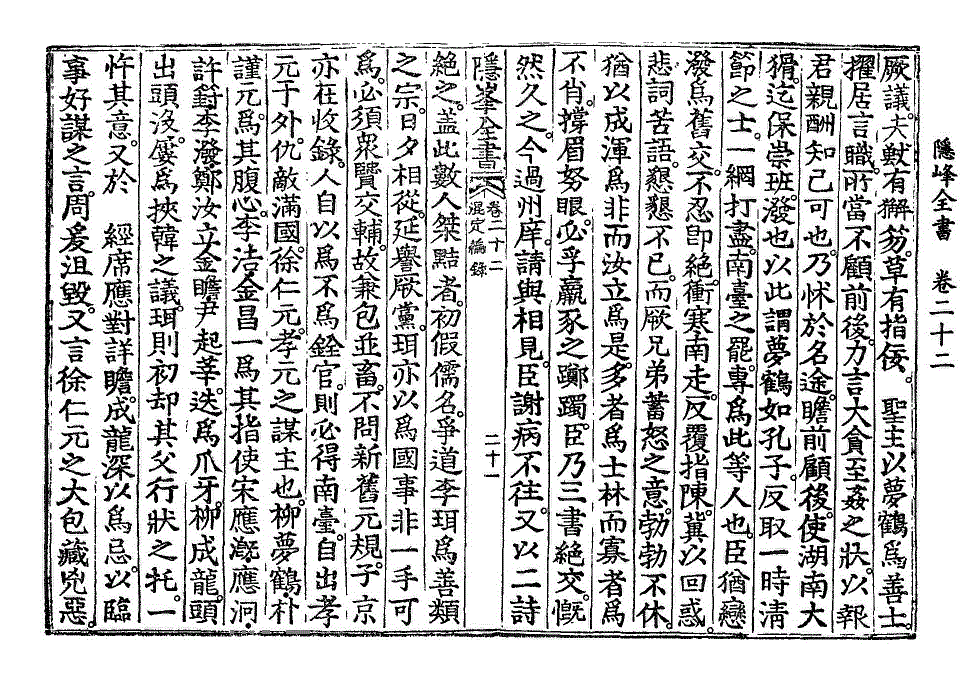 厥议。夫兽有獬笏。草有指佞。 圣主以梦鹤为善士。擢居言职。所当不顾前后。力言大贪至奸之状。以报君亲酬知己可也。乃怵于名途。瞻前顾后。使湖南大猾。迄保崇班。泼也以此谓梦鹤如孔子。反取一时清节之士。一网打尽。南台之罢。专为此等人也。臣犹恋泼为旧交。不忍即绝。冲寒南走。反覆指陈。冀以回惑。悲词苦语。恳恳不已。而厥兄弟蓄怒之意。勃勃不休。犹以成浑为非而汝立为是。多者为士林而寡者为不肖。撑眉努眼。必孚羸豕之踯躅。臣乃三书绝交。慨然久之。今过州庠。请与相见。臣谢病不往。又以二诗绝之。盖此数人桀黠者。初假儒名。争道李珥为善类之宗。日夕相从。延誉厥党。珥亦以为国事非一手可为。必须众贤交辅。故兼包并畜。不问新旧元规。子京亦在收录。人自以为不为铨官。则必得南台。自出孝元于外。仇敌满国。徐仁元。孝元之谋主也。柳梦鹤,朴谨元。为其腹心。李洁,金昌一为其指使宋应溉,应泂,许篈,李泼,郑汝立,金瞻,尹起莘。迭为爪牙。柳成龙。头出头没。屡为挟韩之议。珥则初却其父行状之托。一忤其意。又于 经席应对详瞻。成龙深以为忌。以临事好谋之言。周爰沮毁。又言徐仁元之大包藏凶恶。
厥议。夫兽有獬笏。草有指佞。 圣主以梦鹤为善士。擢居言职。所当不顾前后。力言大贪至奸之状。以报君亲酬知己可也。乃怵于名途。瞻前顾后。使湖南大猾。迄保崇班。泼也以此谓梦鹤如孔子。反取一时清节之士。一网打尽。南台之罢。专为此等人也。臣犹恋泼为旧交。不忍即绝。冲寒南走。反覆指陈。冀以回惑。悲词苦语。恳恳不已。而厥兄弟蓄怒之意。勃勃不休。犹以成浑为非而汝立为是。多者为士林而寡者为不肖。撑眉努眼。必孚羸豕之踯躅。臣乃三书绝交。慨然久之。今过州庠。请与相见。臣谢病不往。又以二诗绝之。盖此数人桀黠者。初假儒名。争道李珥为善类之宗。日夕相从。延誉厥党。珥亦以为国事非一手可为。必须众贤交辅。故兼包并畜。不问新旧元规。子京亦在收录。人自以为不为铨官。则必得南台。自出孝元于外。仇敌满国。徐仁元。孝元之谋主也。柳梦鹤,朴谨元。为其腹心。李洁,金昌一为其指使宋应溉,应泂,许篈,李泼,郑汝立,金瞻,尹起莘。迭为爪牙。柳成龙。头出头没。屡为挟韩之议。珥则初却其父行状之托。一忤其意。又于 经席应对详瞻。成龙深以为忌。以临事好谋之言。周爰沮毁。又言徐仁元之大包藏凶恶。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第 1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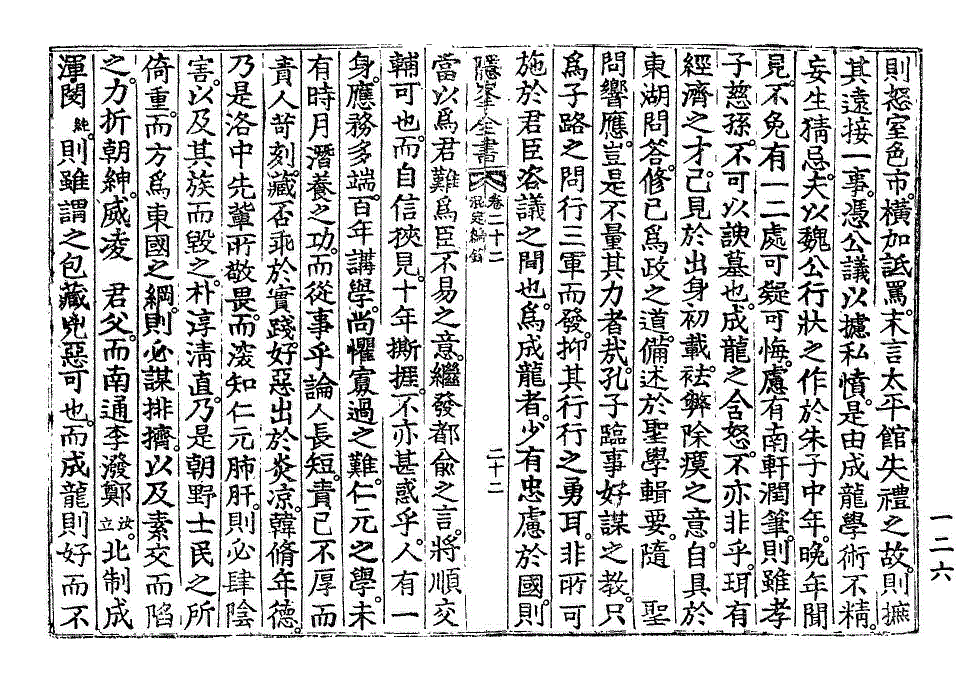 则怒室色市。横加诋骂。末言太平馆失礼之故。则摭其远接一事。凭公议以摅私愤。是由成龙学术不精。妄生猜忌。夫以魏公行状之作于朱子中年。晚年闻见。不免有一二处可疑可悔。虑有南轩润笔。则虽孝子慈孙。不可以谀墓也。成龙之含怒。不亦非乎。珥有经济之才。已见于出身初载。袪弊除瘼之意。自具于东湖问答。修已为政之道。备述于圣学辑要。随 圣问响应。岂是不量其力者哉。孔子临事好谋之教。只为子路之问行三军而发。抑其行行之勇耳。非所可施于君臣咨议之间也。为成龙者。少有忠虑于国。则当以为君难为臣不易之意。继发都俞之言。将顺交辅可也。而自信狭见。十年撕挨。不亦甚惑乎。人有一身。应务多端。百年讲学。尚惧寡过之难。仁元之学。未有时月潜养之功。而从事乎论人长短。责己不厚而责人苛刻。藏否乖于实践。好恶出于炎凉。韩脩年德。乃是洛中先辈所敬畏。而深知仁元肺肝。则必肆阴害。以及其族而毁之。朴淳清直。乃是朝野士民之所倚重。而方为东国之纲。则必谋排挤。以及素交而陷之。力折朝绅。威浚 君父。而南通李泼郑(汝立)。北制成浑,闵(纯)。则虽谓之包藏凶恶可也。而成龙则好而不
则怒室色市。横加诋骂。末言太平馆失礼之故。则摭其远接一事。凭公议以摅私愤。是由成龙学术不精。妄生猜忌。夫以魏公行状之作于朱子中年。晚年闻见。不免有一二处可疑可悔。虑有南轩润笔。则虽孝子慈孙。不可以谀墓也。成龙之含怒。不亦非乎。珥有经济之才。已见于出身初载。袪弊除瘼之意。自具于东湖问答。修已为政之道。备述于圣学辑要。随 圣问响应。岂是不量其力者哉。孔子临事好谋之教。只为子路之问行三军而发。抑其行行之勇耳。非所可施于君臣咨议之间也。为成龙者。少有忠虑于国。则当以为君难为臣不易之意。继发都俞之言。将顺交辅可也。而自信狭见。十年撕挨。不亦甚惑乎。人有一身。应务多端。百年讲学。尚惧寡过之难。仁元之学。未有时月潜养之功。而从事乎论人长短。责己不厚而责人苛刻。藏否乖于实践。好恶出于炎凉。韩脩年德。乃是洛中先辈所敬畏。而深知仁元肺肝。则必肆阴害。以及其族而毁之。朴淳清直。乃是朝野士民之所倚重。而方为东国之纲。则必谋排挤。以及素交而陷之。力折朝绅。威浚 君父。而南通李泼郑(汝立)。北制成浑,闵(纯)。则虽谓之包藏凶恶可也。而成龙则好而不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第 1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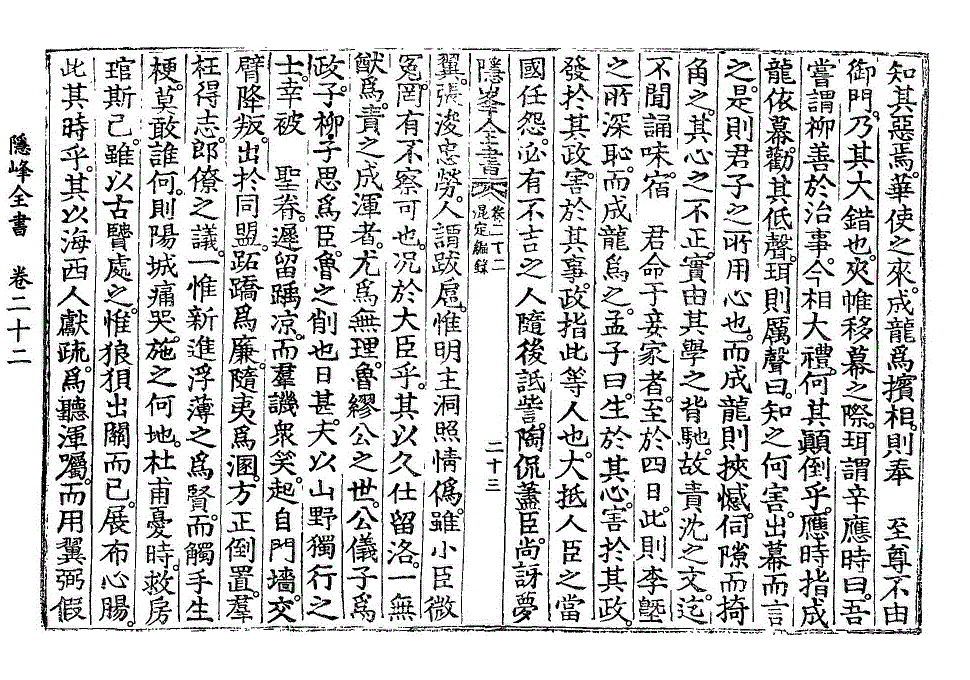 知其恶焉。华使之来。成龙为摈相。则奉 至尊不由御门。乃其大错也。夹帷移幕之际。珥谓辛应时曰。吾尝谓柳善于治事。今相大礼。何其颠倒乎。应时指成龙依幕。劝其低声。珥则厉声曰。知之何害。出幕而言之。是则君子之所用心也。而成龙则挟憾。伺隙而掎角之。其心之不正。实由其学之背驰。故责沈之文。迄不闻诵味。宿 君命于妾家者。至于四日。此则李塈之所深耻。而成龙为之。孟子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政指此等人也。大抵人臣之当国任怨。必有不吉之人随后诋訾。陶侃荩臣。尚讶梦翼。张浚忠劳。人谓跋扈。惟明主洞照情伪。虽小臣微冤。罔有不察可也。况于大臣乎。其以久仕留洛。一无猷为。责之成浑者。尤为无理。鲁缪公之世。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日甚。夫以山野独行之士。幸被 圣眷。迟留踽凉。而群讥众笑。起自门墙。交臂降叛。出于同盟。蹠蹻为廉。随夷为溷。方正倒置。群枉得志。郎僚之议。一惟新进浮薄之为贤。而触手生梗。莫敢谁何。则阳城痛哭。施之何地。杜甫忧时。救房琯斯已。虽以古贤处之。惟狼狈出关而已。展布心肠。此其时乎。其以海西人献疏。为听浑嘱。而用翼弼假
知其恶焉。华使之来。成龙为摈相。则奉 至尊不由御门。乃其大错也。夹帷移幕之际。珥谓辛应时曰。吾尝谓柳善于治事。今相大礼。何其颠倒乎。应时指成龙依幕。劝其低声。珥则厉声曰。知之何害。出幕而言之。是则君子之所用心也。而成龙则挟憾。伺隙而掎角之。其心之不正。实由其学之背驰。故责沈之文。迄不闻诵味。宿 君命于妾家者。至于四日。此则李塈之所深耻。而成龙为之。孟子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政指此等人也。大抵人臣之当国任怨。必有不吉之人随后诋訾。陶侃荩臣。尚讶梦翼。张浚忠劳。人谓跋扈。惟明主洞照情伪。虽小臣微冤。罔有不察可也。况于大臣乎。其以久仕留洛。一无猷为。责之成浑者。尤为无理。鲁缪公之世。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日甚。夫以山野独行之士。幸被 圣眷。迟留踽凉。而群讥众笑。起自门墙。交臂降叛。出于同盟。蹠蹻为廉。随夷为溷。方正倒置。群枉得志。郎僚之议。一惟新进浮薄之为贤。而触手生梗。莫敢谁何。则阳城痛哭。施之何地。杜甫忧时。救房琯斯已。虽以古贤处之。惟狼狈出关而已。展布心肠。此其时乎。其以海西人献疏。为听浑嘱。而用翼弼假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第 1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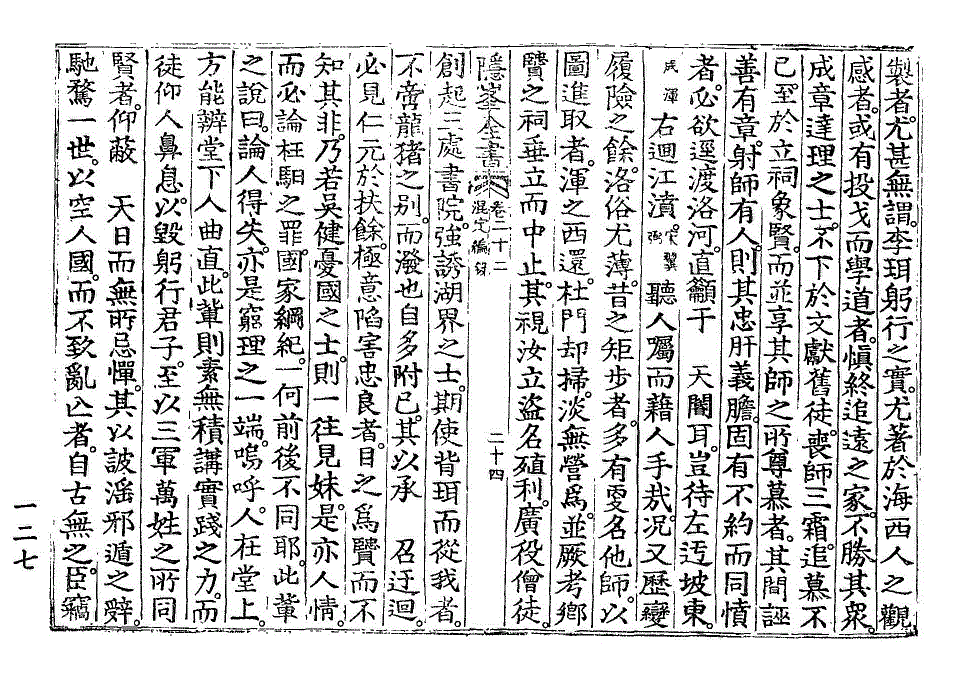 制者。尤甚无谓。李珥躬行之实。尤著于海西人之观感者。或有投戈而学道者。慎终追远之家。不胜其众。成章达理之士。不下于文献旧徒。丧师三霜。追慕不已。至于立祠象贤。而并享其师之所尊慕者。其间诬善有章。射师有人。则其忠肝义胆。固有不约而同愤者。必欲径渡洛河。直吁于 天阍耳。岂待左迂坡东。(成浑)右回江濆。(宋翼弼)听人嘱而藉人手哉。况又历变履险之馀。洛俗尤薄。昔之矩步者。多有更名他师。以图进取者。浑之西还。杜门却扫。淡无营为。并厥考乡贤之祠垂立而中止。其视汝立盗名殖利。广役僧徒。创起三处书院。强诱湖界之士。期使背珥而从我者。不啻龙猪之别。而泼也自多附己。其以承 召迂回。必见仁元于扶馀。极意陷害忠良者。目之为贤而不知其非。乃若吴健忧国之士。则一往见妹。是亦人情。而必论枉驲之罪。国家纲纪。一何前后不同耶。此辈之说曰。论人得失。亦是穷理之一端。呜呼。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此辈则素无积讲实践之力。而徒仰人鼻息。以毁躬行君子。至以三军万姓之所同贤者。仰蔽 天日而无所忌惮。其以诐淫邪遁之辞。驰骛一世。以空人国。而不致乱亡者。自古无之。臣窃
制者。尤甚无谓。李珥躬行之实。尤著于海西人之观感者。或有投戈而学道者。慎终追远之家。不胜其众。成章达理之士。不下于文献旧徒。丧师三霜。追慕不已。至于立祠象贤。而并享其师之所尊慕者。其间诬善有章。射师有人。则其忠肝义胆。固有不约而同愤者。必欲径渡洛河。直吁于 天阍耳。岂待左迂坡东。(成浑)右回江濆。(宋翼弼)听人嘱而藉人手哉。况又历变履险之馀。洛俗尤薄。昔之矩步者。多有更名他师。以图进取者。浑之西还。杜门却扫。淡无营为。并厥考乡贤之祠垂立而中止。其视汝立盗名殖利。广役僧徒。创起三处书院。强诱湖界之士。期使背珥而从我者。不啻龙猪之别。而泼也自多附己。其以承 召迂回。必见仁元于扶馀。极意陷害忠良者。目之为贤而不知其非。乃若吴健忧国之士。则一往见妹。是亦人情。而必论枉驲之罪。国家纲纪。一何前后不同耶。此辈之说曰。论人得失。亦是穷理之一端。呜呼。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此辈则素无积讲实践之力。而徒仰人鼻息。以毁躬行君子。至以三军万姓之所同贤者。仰蔽 天日而无所忌惮。其以诐淫邪遁之辞。驰骛一世。以空人国。而不致乱亡者。自古无之。臣窃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第 1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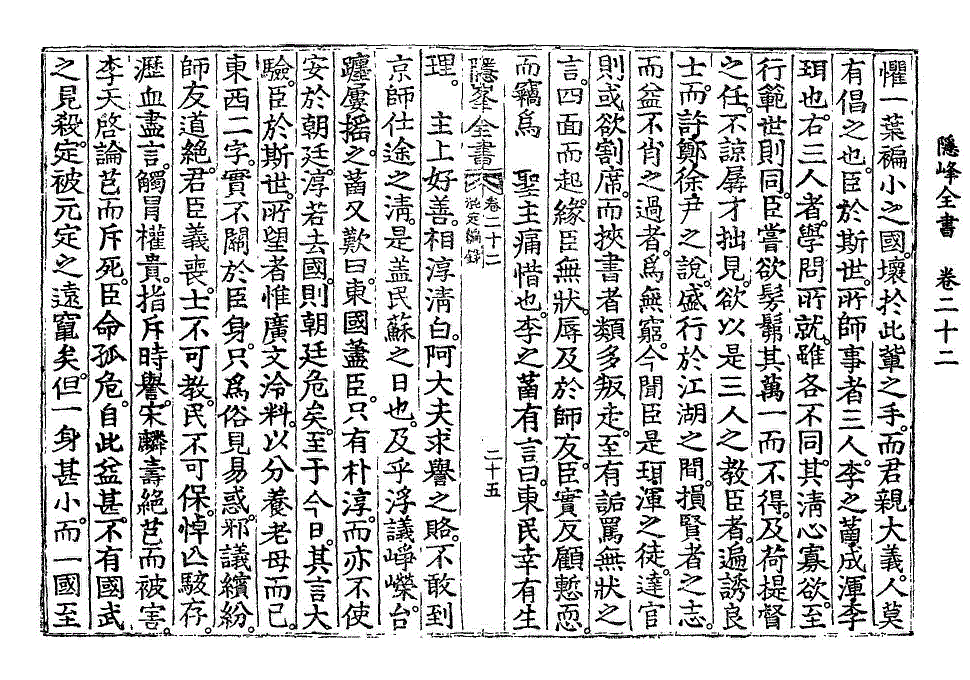 惧一叶褊小之国。坏于此辈之手。而君亲大义。人莫有倡之也。臣于斯世。所师事者三人。李之菡,成浑,李珥也。右三人者。学问所就。虽各不同。其清心寡欲。至行范世则同。臣尝欲髣髴其万一而不得。及荷提督之任。不谅孱才拙见。欲以是三人之教臣者。遍诱良士。而许,郑,徐,尹之说。盛行于江湖之间。损贤者之志。而益不肖之过者。为无穷。今闻臣是珥,浑之徒。达官则或欲割席。而挟书者类多叛走。至有诟骂无状之言。四面而起。缘臣无状。辱及于师友。臣实反顾惭恧。而窃为 圣主痛惜也。李之菡有言曰。东民幸有生理。 主上好善。相淳清白。阿大夫求誉之赂。不敢到京师仕途之清。是盖民苏之日也。及乎浮议峥嵘台躔屡摇。之菡又叹曰。东国荩臣。只有朴淳。而亦不使安于朝廷。淳若去国。则朝廷危矣。至于今日。其言大验。臣于斯世。所望者惟广文泠料。以分养老母而已。东西二字。实不关于臣身。只为俗见易惑。邪议缤纷。师友道绝。君臣义丧。士不可教。民不可保。悼亡骇存。沥血尽言。触冒权贵。指斥时誉。宋麟寿绝芑而被害。李天启论芑而斥死。臣命孤危自此益甚。不有国武之见杀。定被元定之远窜矣。但一身甚小。而一国至
惧一叶褊小之国。坏于此辈之手。而君亲大义。人莫有倡之也。臣于斯世。所师事者三人。李之菡,成浑,李珥也。右三人者。学问所就。虽各不同。其清心寡欲。至行范世则同。臣尝欲髣髴其万一而不得。及荷提督之任。不谅孱才拙见。欲以是三人之教臣者。遍诱良士。而许,郑,徐,尹之说。盛行于江湖之间。损贤者之志。而益不肖之过者。为无穷。今闻臣是珥,浑之徒。达官则或欲割席。而挟书者类多叛走。至有诟骂无状之言。四面而起。缘臣无状。辱及于师友。臣实反顾惭恧。而窃为 圣主痛惜也。李之菡有言曰。东民幸有生理。 主上好善。相淳清白。阿大夫求誉之赂。不敢到京师仕途之清。是盖民苏之日也。及乎浮议峥嵘台躔屡摇。之菡又叹曰。东国荩臣。只有朴淳。而亦不使安于朝廷。淳若去国。则朝廷危矣。至于今日。其言大验。臣于斯世。所望者惟广文泠料。以分养老母而已。东西二字。实不关于臣身。只为俗见易惑。邪议缤纷。师友道绝。君臣义丧。士不可教。民不可保。悼亡骇存。沥血尽言。触冒权贵。指斥时誉。宋麟寿绝芑而被害。李天启论芑而斥死。臣命孤危自此益甚。不有国武之见杀。定被元定之远窜矣。但一身甚小。而一国至隐峰全书卷二十二 第 1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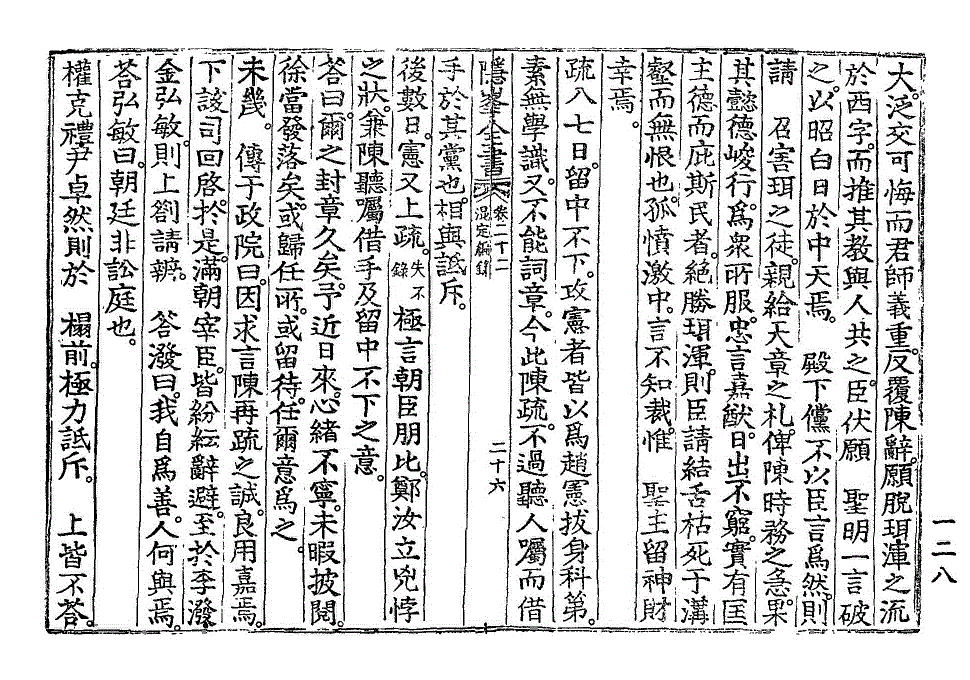 大。泛交可悔而君师义重。反覆陈辞。愿脱珥,浑之流于西字。而推其教与人共之。臣伏愿 圣明一言破之。以昭白日于中天焉。 殿下傥不以臣言为然。则请 召害珥之徒。亲给天章之札。俾陈时务之急。果其懿德峻行。为众所服。忠言嘉猷。日出不穷。实有匡主德而庇斯民者。绝胜珥,浑。则臣请结舌枯死于沟壑而无恨也。孤愤激中。言不知裁。惟 圣主留神财幸焉。
大。泛交可悔而君师义重。反覆陈辞。愿脱珥,浑之流于西字。而推其教与人共之。臣伏愿 圣明一言破之。以昭白日于中天焉。 殿下傥不以臣言为然。则请 召害珥之徒。亲给天章之札。俾陈时务之急。果其懿德峻行。为众所服。忠言嘉猷。日出不穷。实有匡主德而庇斯民者。绝胜珥,浑。则臣请结舌枯死于沟壑而无恨也。孤愤激中。言不知裁。惟 圣主留神财幸焉。疏入七日。留中不下。攻宪者皆以为赵宪拔身科第。素无学识。又不能词章。今此陈疏。不过听人嘱而借手于其党也。相与诋斥。
后数日。宪又上疏。(失不录)极言朝臣朋比。郑汝立凶悖之状。兼陈听嘱借手及留中不下之意。
答曰。尔之封章久矣。予近日来。心绪不宁。未暇披阅。徐当发落矣。或归任所。或留待。任尔意为之。
未几 。传于政院曰。因求言陈再疏之诚。良用嘉焉。下该司回启。于是。满朝宰臣。皆纷纭辞避。至于李泼,金弘敏。则上劄请辨。 答泼曰。我自为善。人何与焉。答弘敏曰。朝廷非讼庭也。
权克礼,尹卓然则于 榻前。极力诋斥。 上皆不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