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x 页
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书
书
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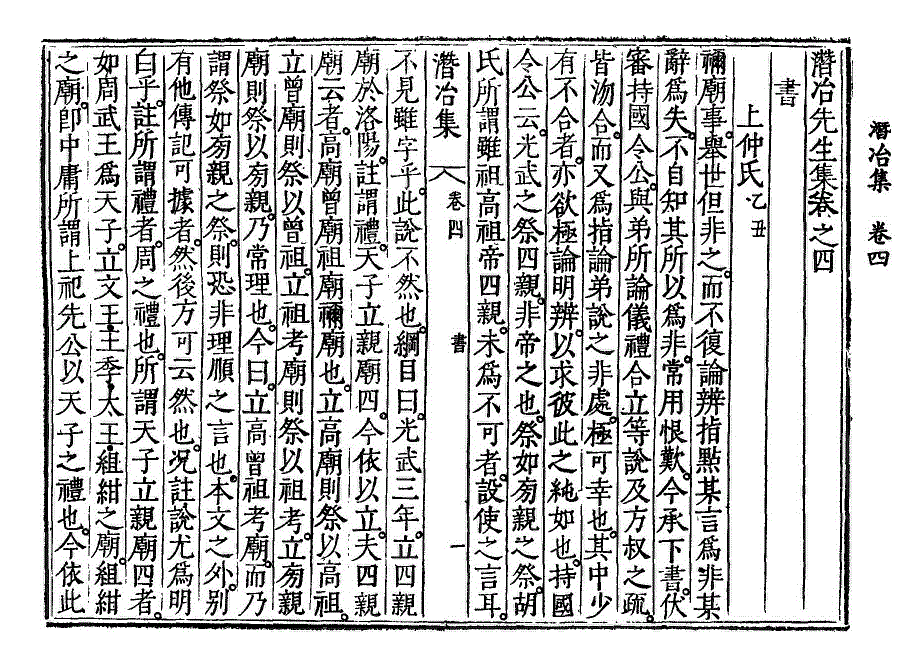 上仲氏(乙丑)
上仲氏(乙丑)祢庙事。举世但非之。而不复论辨指点某言为非某辞为失。不自知其所以为非。常用恨叹。今承下书。伏审持国令公。与弟所论仪礼合立等说及方叔之疏。皆沕合。而又为指论弟说之非处。极可幸也。其中少有不合者。亦欲极论明辨。以求彼此之纯如也。持国令公云。光武之祭四亲。非帝之也。祭如旁亲之祭。胡氏所谓虽祖高祖帝四亲。未为不可者。设使之言耳。不见虽字乎。此说不然也。纲目曰。光武三年。立四亲庙于洛阳。注谓礼。天子立亲庙四。今依以立。夫四亲庙云者。高庙曾庙祖庙祢庙也。立高庙则祭以高祖。立曾庙则祭以曾祖。立祖考庙则祭以祖考。立旁亲庙则祭以旁亲。乃常理也。今曰。立高曾祖考庙。而乃谓祭如旁亲之祭。则恐非理顺之言也。本文之外。别有他传记可据者。然后方可云然也。况注说尤为明白乎。注所谓礼者。周之礼也。所谓天子立亲庙四者。如周武王为天子。立文王,王季,太王,组绀之庙。组绀之庙。即中庸所谓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也。今依此
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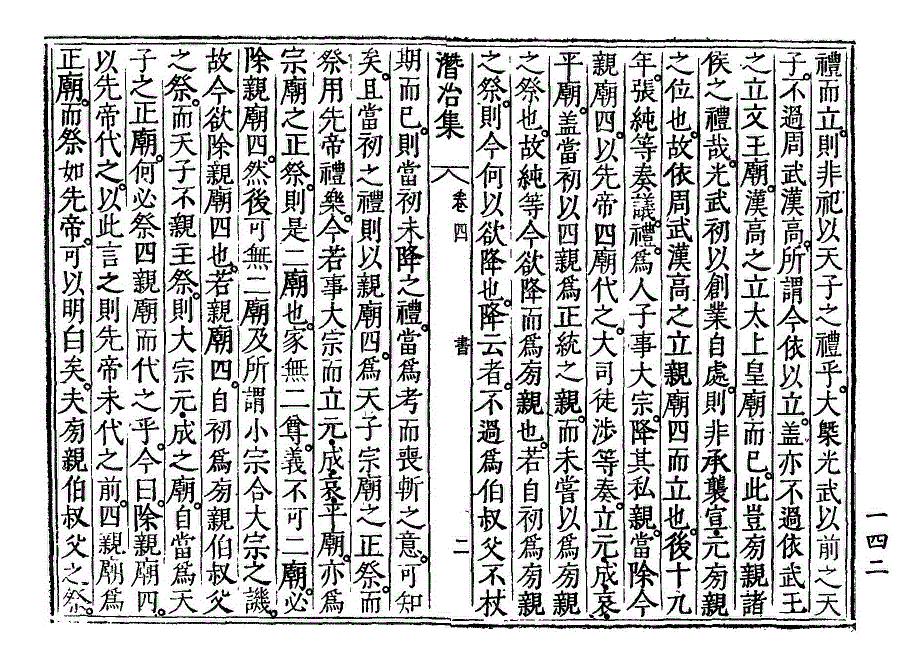 礼而立。则非祀以天子之礼乎。大槩光武以前之天子。不过周武汉高。所谓今依以立。盖亦不过依武王之立文王庙。汉高之立太上皇庙而已。此岂旁亲诸侯之礼哉。光武初以创业自处。则非承袭宣,元旁亲之位也。故依周武汉高之立亲庙四而立也。后十九年。张纯等奏议。礼。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亲。当除今亲庙四。以先帝四庙代之。大司徒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庙。盖当初以四亲为正统之亲。而未尝以为旁亲之祭也。故纯等今欲降而为旁亲也。若自初为旁亲之祭。则今何以欲降也。降云者。不过为伯叔父不杖期而已。则当初未降之礼。当为考而丧斩之意。可知矣。且当初之礼则以亲庙四。为天子宗庙之正祭。而祭用先帝礼乐。今若事大宗而立元,成,哀平庙。亦为宗庙之正祭。则是二庙也。家无二尊。义不可考二庙。必除亲庙四。然后可无二庙及所谓小宗合大宗之讥。故今欲除亲庙四也。若亲庙四。自初为旁亲伯叔父之祭。而天子不亲主祭。则大宗元,成之庙。自当为天子之正庙。何必祭四亲庙而代之乎。今曰。除亲庙四。以先帝代之。以此言之则先帝未代之前。四亲庙为正庙。而祭如先帝。可以明白矣。夫旁亲伯叔父之祭。
礼而立。则非祀以天子之礼乎。大槩光武以前之天子。不过周武汉高。所谓今依以立。盖亦不过依武王之立文王庙。汉高之立太上皇庙而已。此岂旁亲诸侯之礼哉。光武初以创业自处。则非承袭宣,元旁亲之位也。故依周武汉高之立亲庙四而立也。后十九年。张纯等奏议。礼。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亲。当除今亲庙四。以先帝四庙代之。大司徒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庙。盖当初以四亲为正统之亲。而未尝以为旁亲之祭也。故纯等今欲降而为旁亲也。若自初为旁亲之祭。则今何以欲降也。降云者。不过为伯叔父不杖期而已。则当初未降之礼。当为考而丧斩之意。可知矣。且当初之礼则以亲庙四。为天子宗庙之正祭。而祭用先帝礼乐。今若事大宗而立元,成,哀平庙。亦为宗庙之正祭。则是二庙也。家无二尊。义不可考二庙。必除亲庙四。然后可无二庙及所谓小宗合大宗之讥。故今欲除亲庙四也。若亲庙四。自初为旁亲伯叔父之祭。而天子不亲主祭。则大宗元,成之庙。自当为天子之正庙。何必祭四亲庙而代之乎。今曰。除亲庙四。以先帝代之。以此言之则先帝未代之前。四亲庙为正庙。而祭如先帝。可以明白矣。夫旁亲伯叔父之祭。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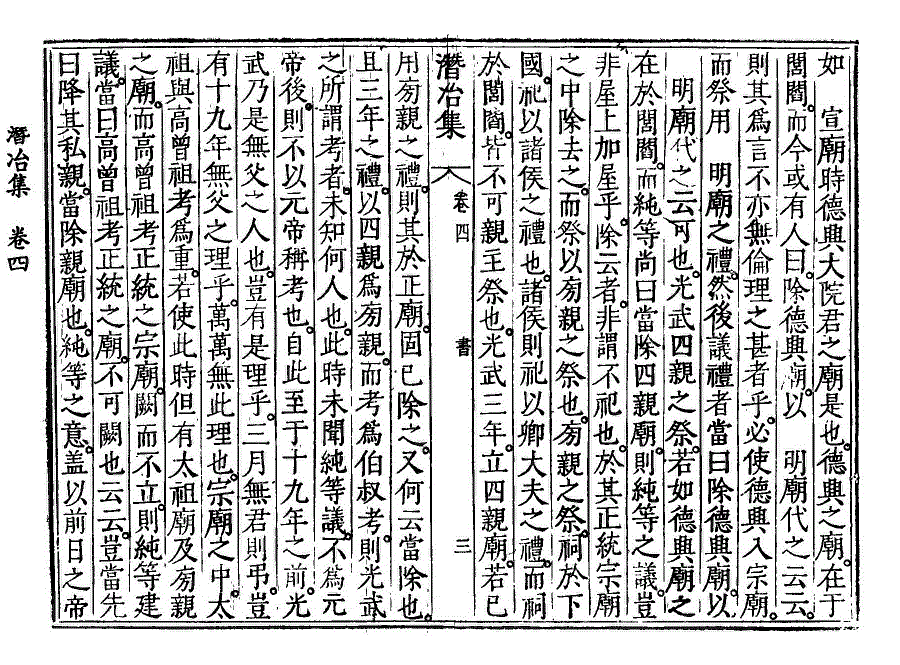 如 宣庙时德兴大院君之庙是也。德兴之庙。在于闾阎。而今或有人曰。除德兴庙。以 明庙代之云云。则其为言不亦无伦理之甚者乎。必使德兴入宗庙。而祭用 明庙之礼。然后议礼者当曰除德兴庙。以 明庙代之云可也。光武四亲之祭。若如德兴庙之在于闾阎。而纯等尚曰当除四亲庙。则纯等之议。岂非屋上加屋乎。除云者。非谓不祀也。于其正统宗庙之中除去之。而祭以旁亲之祭也。旁亲之祭。祠于下国。祀以诸侯之礼也。诸侯则祀以卿大夫之礼。而祠于闾阎。皆不可亲主祭也。光武三年。立四亲庙。若已用旁亲之礼。则其于正庙。固已除之。又何云当除也。且三年之礼。以四亲为旁亲。而考为伯叔考。则光武之所谓考者。未知何人也。此时未闻纯等议。不为元帝后。则不以元帝称考也。自此至于十九年之前。光武乃是无父之人也。岂有是理乎。三月无君则吊。岂有十九年无父之理乎。万万无此理也。宗庙之中。太祖与高曾祖考为重。若使此时但有太祖庙及旁亲之庙。而高曾祖考正统之宗庙。阙而不立。则纯等建议。当曰高曾祖考正统之庙。不可阙也云云。岂当先曰降其私亲。当除亲庙也。纯等之意。盖以前日之帝
如 宣庙时德兴大院君之庙是也。德兴之庙。在于闾阎。而今或有人曰。除德兴庙。以 明庙代之云云。则其为言不亦无伦理之甚者乎。必使德兴入宗庙。而祭用 明庙之礼。然后议礼者当曰除德兴庙。以 明庙代之云可也。光武四亲之祭。若如德兴庙之在于闾阎。而纯等尚曰当除四亲庙。则纯等之议。岂非屋上加屋乎。除云者。非谓不祀也。于其正统宗庙之中除去之。而祭以旁亲之祭也。旁亲之祭。祠于下国。祀以诸侯之礼也。诸侯则祀以卿大夫之礼。而祠于闾阎。皆不可亲主祭也。光武三年。立四亲庙。若已用旁亲之礼。则其于正庙。固已除之。又何云当除也。且三年之礼。以四亲为旁亲。而考为伯叔考。则光武之所谓考者。未知何人也。此时未闻纯等议。不为元帝后。则不以元帝称考也。自此至于十九年之前。光武乃是无父之人也。岂有是理乎。三月无君则吊。岂有十九年无父之理乎。万万无此理也。宗庙之中。太祖与高曾祖考为重。若使此时但有太祖庙及旁亲之庙。而高曾祖考正统之宗庙。阙而不立。则纯等建议。当曰高曾祖考正统之庙。不可阙也云云。岂当先曰降其私亲。当除亲庙也。纯等之意。盖以前日之帝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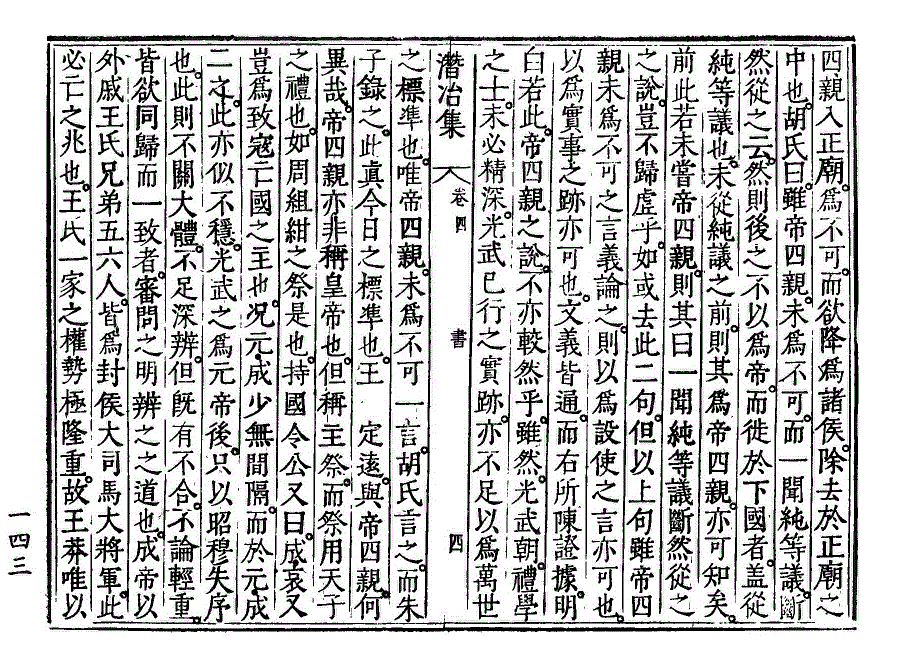 四亲入正庙。为不可。而欲降为诸侯。除去于正庙之中也。胡氏曰。虽帝四亲。未为不可。而一闻纯等议。断然从之云。然则后之不以为帝。而徙于下国者。盖从纯等议也。未从纯议之前。则其为帝四亲。亦可知矣。前此若未尝帝四亲。则其曰一闻纯等议断然从之之说。岂不归虚乎。如或去此二句。但以上句虽帝四亲未为不可之言义论之。则以为设使之言亦可也。以为实事之迹亦可也。文义皆通。而右所陈證据。明白若此。帝四亲之说。不亦较然乎。虽然。光武朝。礼学之士。未必精深。光武已行之实迹。亦不足以为万世之标准也。唯帝四亲。未为不可一言。胡氏言之。而朱子录之。此真今日之标准也。王 定远。与帝四亲。何异哉。帝四亲亦非称皇帝也。但称主祭。而祭用天子之礼也。如周组绀之祭是也。持国令公又曰。成,哀又岂为致寇亡国之主也。况元,成少无间隔。而于元,成二之。此亦似不稳。光武之为元帝后。只以昭穆失序也。此则不关大体。不足深辨。但既有不合。不论轻重。皆欲同归而一致者。审问之明辨之之道也。成帝以外戚王氏兄弟五六人。皆为封侯大司马大将军。此必亡之兆也。王氏一家之权势极隆重。故王莽唯以
四亲入正庙。为不可。而欲降为诸侯。除去于正庙之中也。胡氏曰。虽帝四亲。未为不可。而一闻纯等议。断然从之云。然则后之不以为帝。而徙于下国者。盖从纯等议也。未从纯议之前。则其为帝四亲。亦可知矣。前此若未尝帝四亲。则其曰一闻纯等议断然从之之说。岂不归虚乎。如或去此二句。但以上句虽帝四亲未为不可之言义论之。则以为设使之言亦可也。以为实事之迹亦可也。文义皆通。而右所陈證据。明白若此。帝四亲之说。不亦较然乎。虽然。光武朝。礼学之士。未必精深。光武已行之实迹。亦不足以为万世之标准也。唯帝四亲。未为不可一言。胡氏言之。而朱子录之。此真今日之标准也。王 定远。与帝四亲。何异哉。帝四亲亦非称皇帝也。但称主祭。而祭用天子之礼也。如周组绀之祭是也。持国令公又曰。成,哀又岂为致寇亡国之主也。况元,成少无间隔。而于元,成二之。此亦似不稳。光武之为元帝后。只以昭穆失序也。此则不关大体。不足深辨。但既有不合。不论轻重。皆欲同归而一致者。审问之明辨之之道也。成帝以外戚王氏兄弟五六人。皆为封侯大司马大将军。此必亡之兆也。王氏一家之权势极隆重。故王莽唯以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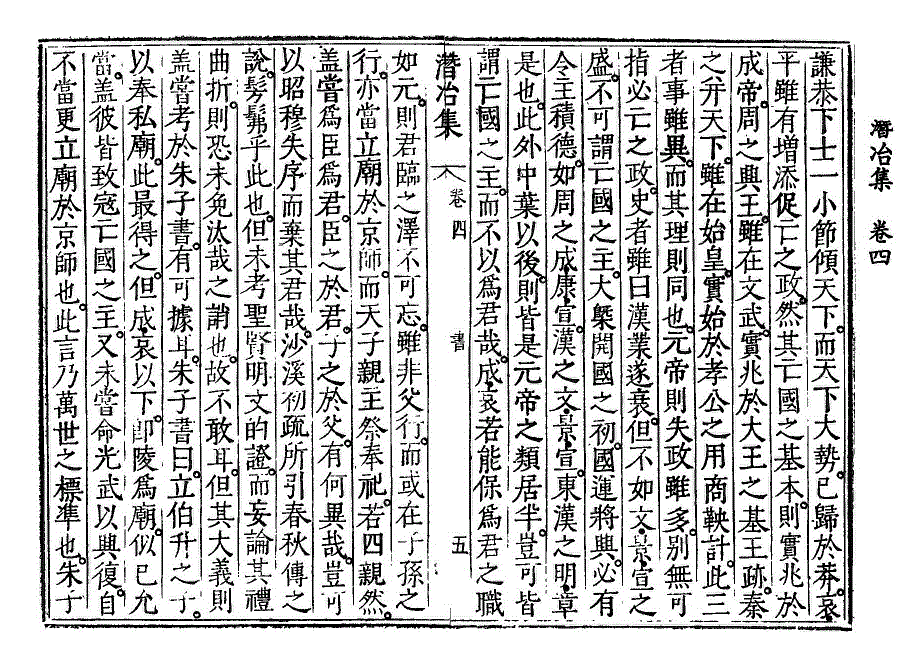 谦恭下士一小节倾天下。而天下大势。已归于莽。哀,平虽有增添促亡之政。然其亡国之基本。则实兆于成帝。周之兴王。虽在文武。实兆于大王之基王迹。秦之并天下。虽在始皇。实始于孝公之用商鞅计。此三者事虽异。而其理则同也。元帝则失政虽多。别无可指必亡之政。史者虽曰汉业遂衰。但不如文,景,宣之盛。不可谓亡国之主。大槩开国之初。国运将兴。必有令主积德。如周之成,康,宣。汉之文,景,宣。东汉之明,章是也。此外中叶以后。则皆是元帝之类居半。岂可皆谓亡国之主。而不以为君哉。成,哀若能保为君之职如元。则君临之泽不可忘。虽非父行。而或在子孙之行。亦当立庙于京师。而天子亲主祭奉祀。若四亲然。盖尝为臣为君。臣之于君。子之于父。有何异哉。岂可以昭穆失序而弃其君哉。沙溪初疏所引春秋传之说。髣髴乎此也。但未考圣贤明文的證。而妄论其礼曲折。则恐未免汰哉之诮也。故不敢耳。但其大义则盖尝考于朱子书。有可据耳。朱子书曰。立伯升之子。以奉私庙。此最得之。但成,哀以下。即陵为庙。似已允当。盖彼皆致寇亡国之主。又未尝命光武以兴复。自不当更立庙于京师也。此言乃万世之标准也。朱子
谦恭下士一小节倾天下。而天下大势。已归于莽。哀,平虽有增添促亡之政。然其亡国之基本。则实兆于成帝。周之兴王。虽在文武。实兆于大王之基王迹。秦之并天下。虽在始皇。实始于孝公之用商鞅计。此三者事虽异。而其理则同也。元帝则失政虽多。别无可指必亡之政。史者虽曰汉业遂衰。但不如文,景,宣之盛。不可谓亡国之主。大槩开国之初。国运将兴。必有令主积德。如周之成,康,宣。汉之文,景,宣。东汉之明,章是也。此外中叶以后。则皆是元帝之类居半。岂可皆谓亡国之主。而不以为君哉。成,哀若能保为君之职如元。则君临之泽不可忘。虽非父行。而或在子孙之行。亦当立庙于京师。而天子亲主祭奉祀。若四亲然。盖尝为臣为君。臣之于君。子之于父。有何异哉。岂可以昭穆失序而弃其君哉。沙溪初疏所引春秋传之说。髣髴乎此也。但未考圣贤明文的證。而妄论其礼曲折。则恐未免汰哉之诮也。故不敢耳。但其大义则盖尝考于朱子书。有可据耳。朱子书曰。立伯升之子。以奉私庙。此最得之。但成,哀以下。即陵为庙。似已允当。盖彼皆致寇亡国之主。又未尝命光武以兴复。自不当更立庙于京师也。此言乃万世之标准也。朱子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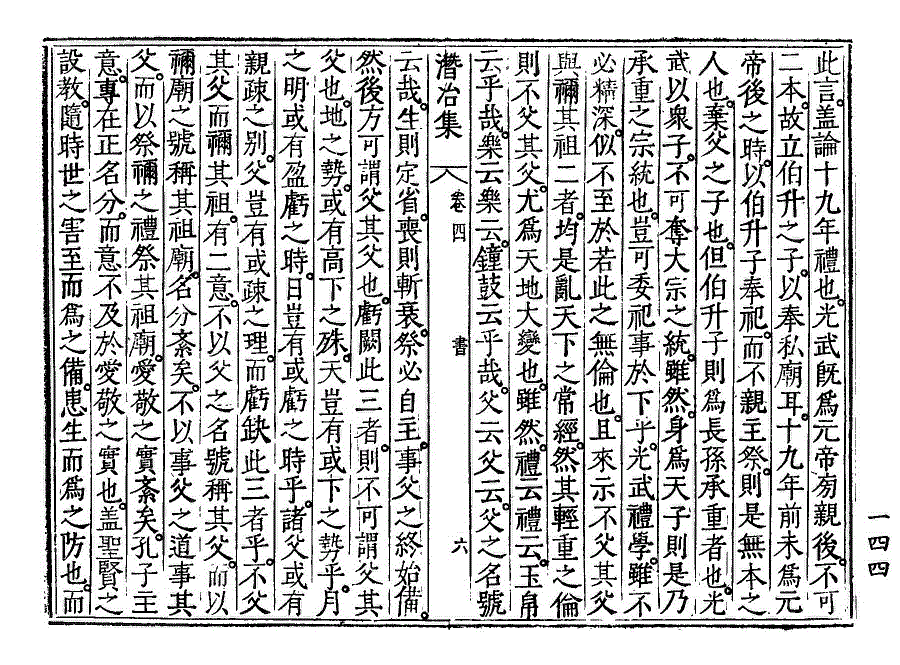 此言。盖论十九年礼也。光武既为元帝旁亲后。不可二本。故立伯升之子。以奉私庙耳。十九年前未为元帝后之时。以伯升子奉祀。而不亲主祭。则是无本之人也。弃父之子也。但伯升子则为长孙承重者也。光武以众子。不可夺大宗之统。虽然。身为天子则是乃承重之宗统也。岂可委祀事于下乎。光武礼学。虽不必精深。似不至于若此之无伦也。且来示不父其父与祢其祖二者。均是乱天下之常经。然其轻重之伦则不父其父。尤为天地大变也。虽然。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父云父云。父之名号云哉。生则定省。丧则斩衰。祭必自主。事父之终始备。然后方可谓父其父也。亏阙此三者。则不可谓父其父也。地之势。或有高下之殊。天岂有或下之势乎。月之明或有盈亏之时。日岂有或亏之时乎。诸父或有亲疏之别。父岂有或疏之理。而亏缺此三者乎。不父其父而祢其祖。有二意。不以父之名号称其父。而以祢庙之号称其祖庙。名分紊矣。不以事父之道事其父。而以祭祢之礼祭其祖庙。爱敬之实紊矣。孔子主意。专在正名分。而意不及于爱敬之实也。盖圣贤之设教。随时世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也。而
此言。盖论十九年礼也。光武既为元帝旁亲后。不可二本。故立伯升之子。以奉私庙耳。十九年前未为元帝后之时。以伯升子奉祀。而不亲主祭。则是无本之人也。弃父之子也。但伯升子则为长孙承重者也。光武以众子。不可夺大宗之统。虽然。身为天子则是乃承重之宗统也。岂可委祀事于下乎。光武礼学。虽不必精深。似不至于若此之无伦也。且来示不父其父与祢其祖二者。均是乱天下之常经。然其轻重之伦则不父其父。尤为天地大变也。虽然。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父云父云。父之名号云哉。生则定省。丧则斩衰。祭必自主。事父之终始备。然后方可谓父其父也。亏阙此三者。则不可谓父其父也。地之势。或有高下之殊。天岂有或下之势乎。月之明或有盈亏之时。日岂有或亏之时乎。诸父或有亲疏之别。父岂有或疏之理。而亏缺此三者乎。不父其父而祢其祖。有二意。不以父之名号称其父。而以祢庙之号称其祖庙。名分紊矣。不以事父之道事其父。而以祭祢之礼祭其祖庙。爱敬之实紊矣。孔子主意。专在正名分。而意不及于爱敬之实也。盖圣贤之设教。随时世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也。而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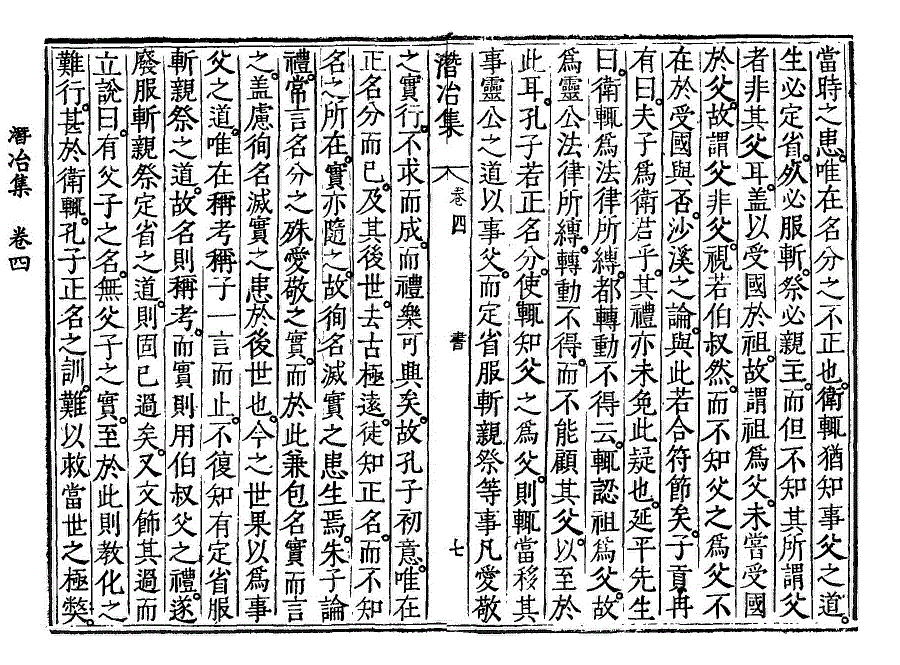 当时之患。唯在名分之不正也。卫辄犹知事父之道。生必定省。死必服斩。祭必亲主。而但不知其所谓父者非其父耳。盖以受国于祖。故谓祖为父。未尝受国于父。故谓父非父。视若伯叔然。而不知父之为父不在于受国与否。沙溪之论。与此若合符节矣。子贡,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其礼亦未免此疑也。延平先生曰。卫辄为法律所縳。都转动不得云。辄认祖为父。故为灵公法律所縳。转动不得。而不能顾其父。以至于此耳。孔子若正名分。使辄知父之为父。则辄当移其事灵公之道以事父。而定省服斩亲祭等事凡爱敬之实行。不求而成。而礼乐可兴矣。故孔子初意。唯在正名分而已。及其后世。去古极远。徒知正名。而不知名之所在。实亦随之。故徇名灭实之患生焉。朱子论礼。常言名分之殊爱敬之实。而于此兼包名实而言之。盖虑徇名灭实之患于后世也。今之世果以为事父之道。唯在称考称子一言而止。不复知有定省服斩亲祭之道。故名则称考。而实则用伯叔父之礼。遂废服斩亲祭定省之道。则固已过矣。又文饰其过而立说曰。有父子之名。无父子之实。至于此则教化之难行。甚于卫辄。孔子正名之训。难以救当世之极弊。
当时之患。唯在名分之不正也。卫辄犹知事父之道。生必定省。死必服斩。祭必亲主。而但不知其所谓父者非其父耳。盖以受国于祖。故谓祖为父。未尝受国于父。故谓父非父。视若伯叔然。而不知父之为父不在于受国与否。沙溪之论。与此若合符节矣。子贡,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其礼亦未免此疑也。延平先生曰。卫辄为法律所縳。都转动不得云。辄认祖为父。故为灵公法律所縳。转动不得。而不能顾其父。以至于此耳。孔子若正名分。使辄知父之为父。则辄当移其事灵公之道以事父。而定省服斩亲祭等事凡爱敬之实行。不求而成。而礼乐可兴矣。故孔子初意。唯在正名分而已。及其后世。去古极远。徒知正名。而不知名之所在。实亦随之。故徇名灭实之患生焉。朱子论礼。常言名分之殊爱敬之实。而于此兼包名实而言之。盖虑徇名灭实之患于后世也。今之世果以为事父之道。唯在称考称子一言而止。不复知有定省服斩亲祭之道。故名则称考。而实则用伯叔父之礼。遂废服斩亲祭定省之道。则固已过矣。又文饰其过而立说曰。有父子之名。无父子之实。至于此则教化之难行。甚于卫辄。孔子正名之训。难以救当世之极弊。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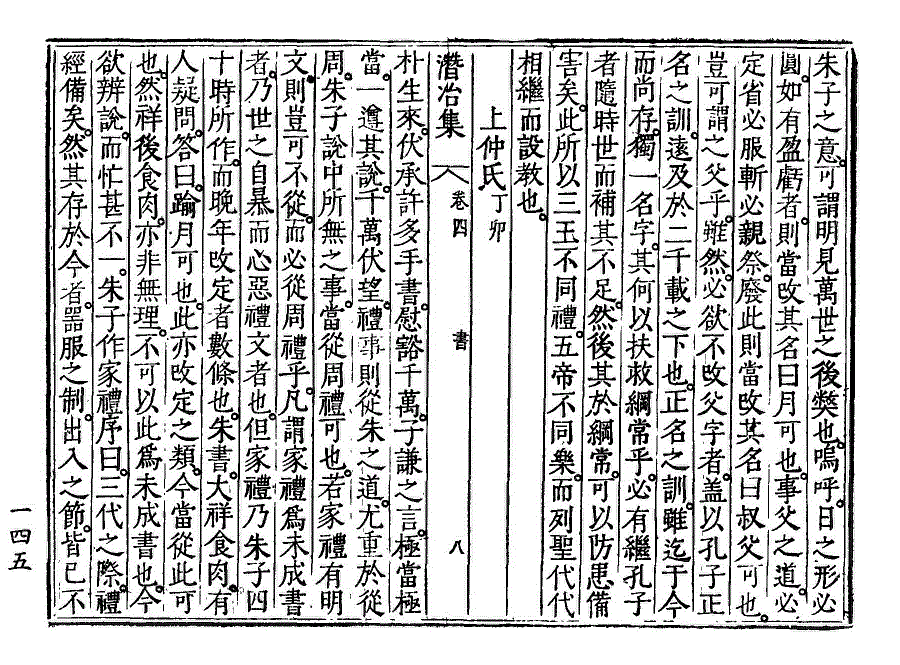 朱子之意。可谓明见万世之后弊也。呜呼。日之形必圆。如有盈亏者。则当改其名曰月可也。事父之道。必定省必服斩必亲祭。废此则当改其名曰叔父可也。岂可谓之父乎。虽然。必欲不改父字者。盖以孔子正名之训。远及于二千载之下也。正名之训。虽迄于今而尚存。独一名字。其何以扶救纲常乎。必有继孔子者随时世而补其不足。然后其于纲常。可以防患备害矣。此所以三王不同礼。五帝不同乐。而列圣代代相继而设教也。
朱子之意。可谓明见万世之后弊也。呜呼。日之形必圆。如有盈亏者。则当改其名曰月可也。事父之道。必定省必服斩必亲祭。废此则当改其名曰叔父可也。岂可谓之父乎。虽然。必欲不改父字者。盖以孔子正名之训。远及于二千载之下也。正名之训。虽迄于今而尚存。独一名字。其何以扶救纲常乎。必有继孔子者随时世而补其不足。然后其于纲常。可以防患备害矣。此所以三王不同礼。五帝不同乐。而列圣代代相继而设教也。上仲氏(丁卯)
朴生来。伏承许多手书。慰豁千万。子谦之言。极当极当。一遵其说。千万伏望。礼事则从朱之道。尤重于从周。朱子说中所无之事。当从周礼可也。若家礼有明文。则岂可不从。而必从周礼乎。凡谓家礼为未成书者。乃世之自暴而心恶礼文者也。但家礼乃朱子四十时所作。而晚年改定者数条也。朱书。大祥食肉。有人疑问。答曰。踰月可也。此亦改定之类。今当从此可也。然祥后食肉。亦非无理。不可以此为未成书也。今欲辨说。而忙甚不一。朱子作家礼序曰。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器服之制。出入之节。皆已不
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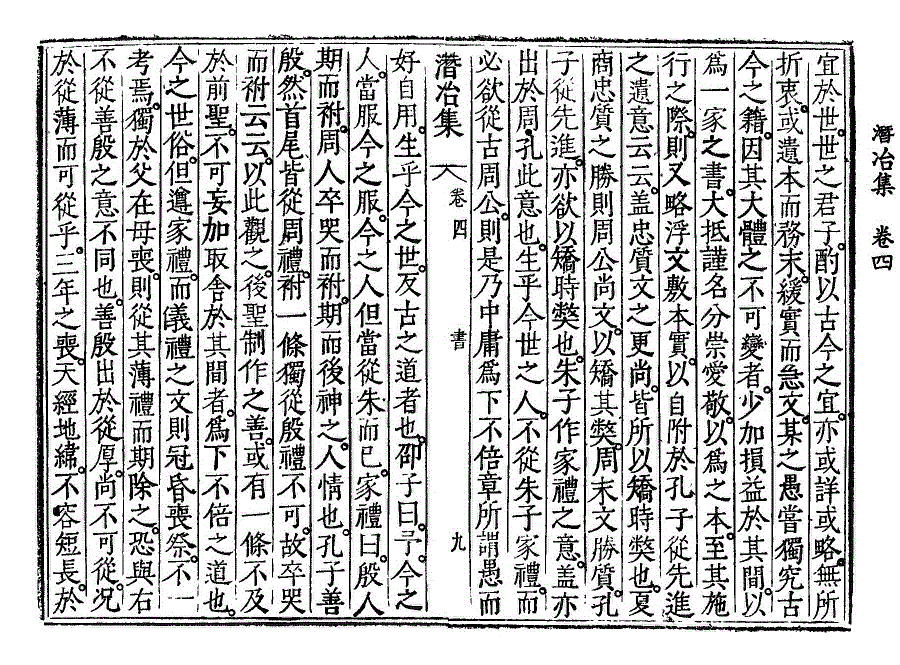 宜于世。世之君子。酌以古今之宜。亦或详或略。无所折衷。或遗本而务末。缓实而急文。某之愚尝独究古今之籍。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少加损益于其间。以为一家之书。大抵谨名分崇爱敬。以为之本。至其施行之际。则又略浮文敷本实。以自附于孔子从先进之遗意云云。盖忠质文之更尚。皆所以矫时弊也。夏商忠质之胜则周公尚文。以矫其弊。周末文胜质。孔子从先进。亦欲以矫时弊也。朱子作家礼之意。盖亦出于周,孔此意也。生乎今世之人。不从朱子家礼。而必欲从古周公。则是乃中庸为下不倍章所谓愚而好自用。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者也。卲子曰。予。今之人。当服今之服。今之人但当从朱而已。家礼曰。殷人期而祔。周人卒哭而祔。期而后神之。人情也。孔子善殷。然首尾皆从周礼。祔一条独从殷礼不可。故卒哭而祔云云。以此观之。后圣制作之善。或有一条不及于前圣。不可妄加取舍于其间者。为下不倍之道也。今之世俗。但遵家礼。而仪礼之文则冠昏丧祭。不一考焉。独于父在母丧。则从其薄礼而期除之。恐与右不从善殷之意不同也。善殷出于从厚。尚不可从。况于从薄而可从乎。三年之丧。天经地纬。不容短长。于
宜于世。世之君子。酌以古今之宜。亦或详或略。无所折衷。或遗本而务末。缓实而急文。某之愚尝独究古今之籍。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少加损益于其间。以为一家之书。大抵谨名分崇爱敬。以为之本。至其施行之际。则又略浮文敷本实。以自附于孔子从先进之遗意云云。盖忠质文之更尚。皆所以矫时弊也。夏商忠质之胜则周公尚文。以矫其弊。周末文胜质。孔子从先进。亦欲以矫时弊也。朱子作家礼之意。盖亦出于周,孔此意也。生乎今世之人。不从朱子家礼。而必欲从古周公。则是乃中庸为下不倍章所谓愚而好自用。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者也。卲子曰。予。今之人。当服今之服。今之人但当从朱而已。家礼曰。殷人期而祔。周人卒哭而祔。期而后神之。人情也。孔子善殷。然首尾皆从周礼。祔一条独从殷礼不可。故卒哭而祔云云。以此观之。后圣制作之善。或有一条不及于前圣。不可妄加取舍于其间者。为下不倍之道也。今之世俗。但遵家礼。而仪礼之文则冠昏丧祭。不一考焉。独于父在母丧。则从其薄礼而期除之。恐与右不从善殷之意不同也。善殷出于从厚。尚不可从。况于从薄而可从乎。三年之丧。天经地纬。不容短长。于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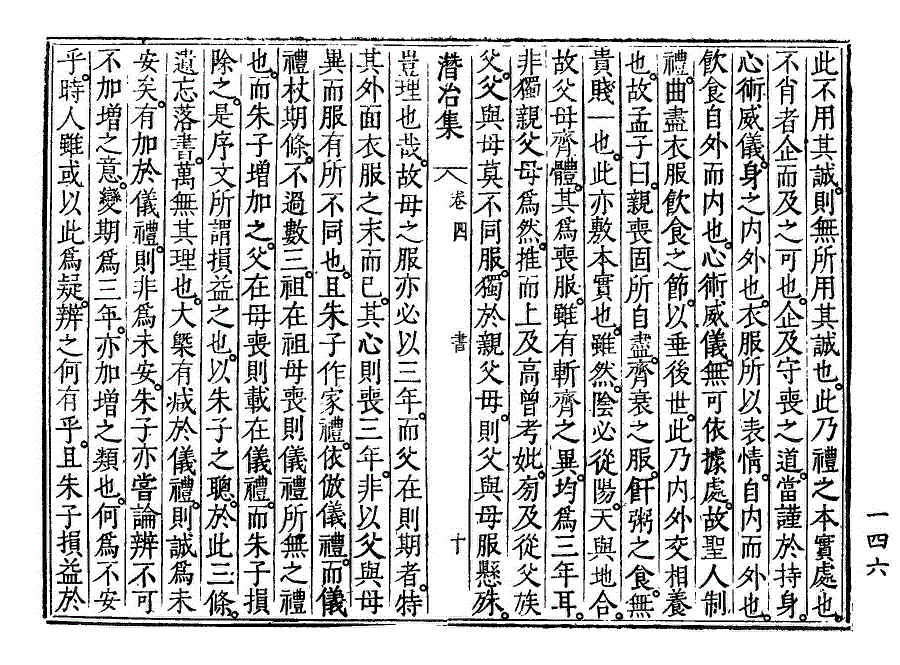 此不用其诚。则无所用其诚也。此乃礼之本实处也。不肖者企而及之可也。企及守丧之道。当谨于持身。心术威仪。身之内外也。衣服所以表情。自内而外也。饮食自外而内也。心术威仪。无可依据处。故圣人制礼。曲尽衣服饮食之节。以垂后世。此乃内外交相养也。故孟子曰。亲丧固所自尽。齐衰之服。饘粥之食。无贵贱一也。此亦敷本实也。虽然。阴必从阳。天与地合。故父母齐体。其为丧服。虽有斩齐之异。均为三年耳。非独亲父母为然。推而上及高曾考妣。旁及从父族父。父与母莫不同服。独于亲父母。则父与母服悬殊。岂理也哉。故母之服亦必以三年。而父在则期者。特其外面衣服之末而已。其心则丧三年。非以父与母异而服有所不同也。且朱子作家礼。依仿仪礼。而仪礼杖期条。不过数三。祖在祖母丧则仪礼所无之礼也。而朱子增加之。父在母丧则载在仪礼。而朱子损除之。是序文所谓损益之也。以朱子之聪。于此三条。遗忘落书。万无其理也。大槩有减于仪礼。则诚为未安矣。有加于仪礼。则非为未安。朱子亦尝论辨不可不加增之意。变期为三年。亦加增之类也。何为不安乎。时人虽或以此为疑辨之何有乎。且朱子损益于
此不用其诚。则无所用其诚也。此乃礼之本实处也。不肖者企而及之可也。企及守丧之道。当谨于持身。心术威仪。身之内外也。衣服所以表情。自内而外也。饮食自外而内也。心术威仪。无可依据处。故圣人制礼。曲尽衣服饮食之节。以垂后世。此乃内外交相养也。故孟子曰。亲丧固所自尽。齐衰之服。饘粥之食。无贵贱一也。此亦敷本实也。虽然。阴必从阳。天与地合。故父母齐体。其为丧服。虽有斩齐之异。均为三年耳。非独亲父母为然。推而上及高曾考妣。旁及从父族父。父与母莫不同服。独于亲父母。则父与母服悬殊。岂理也哉。故母之服亦必以三年。而父在则期者。特其外面衣服之末而已。其心则丧三年。非以父与母异而服有所不同也。且朱子作家礼。依仿仪礼。而仪礼杖期条。不过数三。祖在祖母丧则仪礼所无之礼也。而朱子增加之。父在母丧则载在仪礼。而朱子损除之。是序文所谓损益之也。以朱子之聪。于此三条。遗忘落书。万无其理也。大槩有减于仪礼。则诚为未安矣。有加于仪礼。则非为未安。朱子亦尝论辨不可不加增之意。变期为三年。亦加增之类也。何为不安乎。时人虽或以此为疑辨之何有乎。且朱子损益于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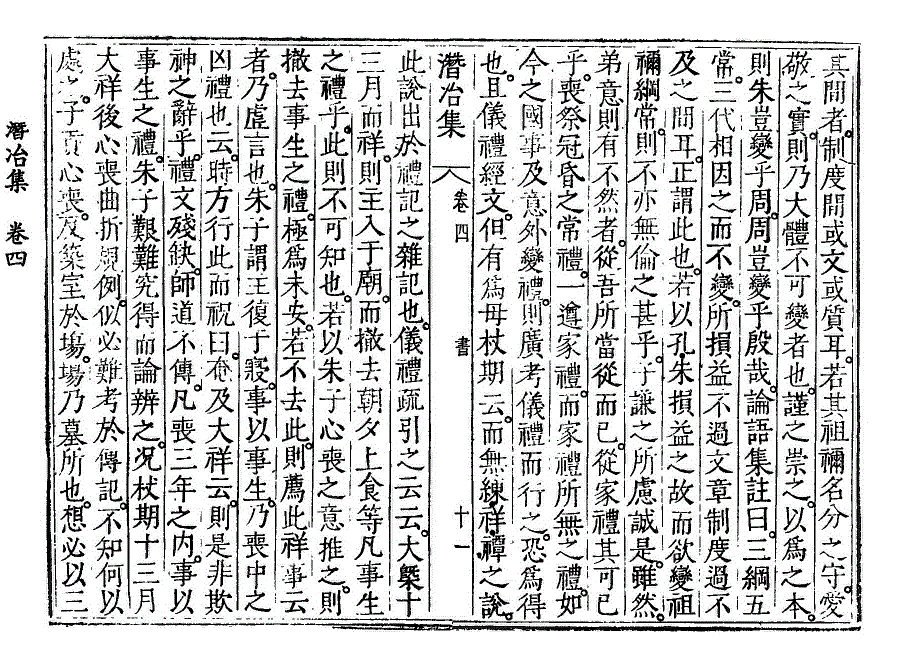 其间者。制度间或文或质耳。若其祖祢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则乃大体不可变者也。谨之崇之。以为之本。则朱岂变乎周。周岂变乎殷哉。论语集注曰。三纲五常。三代相因之而不变。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过不及之间耳。正谓此也。若以孔,朱损益之故而欲变祖祢纲常。则不亦无伦之甚乎。子谦之所虑诚是。虽然。弟意则有不然者。从吾所当从而已。从家礼其可已乎。丧祭冠昏之常礼。一遵家礼。而家礼所无之礼。如今之国事及意外变礼。则广考仪礼而行之。恐为得也。且仪礼经文但有为母杖期云。而无练,祥,禫之说。此说出于礼记之杂记也。仪礼疏引之云云。大槩十三月而祥。则主入于庙。而撤去朝夕上食等凡事生之礼乎。此则不可知也。若以朱子心丧之意推之。则撤去事生之礼。极为未安。若不去此。则荐此祥事云者。乃虚言也。朱子谓主复于寝。事以事生。乃丧中之凶礼也云。时方行此而祝曰。奄及大祥云。则是非欺神之辞乎。礼文残缺。师道不传。凡丧三年之内。事以事生之礼。朱子艰难究得而论辨之。况杖期十三月大祥后心丧曲折规例。似必难考于传记。不知何以处之。子贡心丧。反筑室于场。场乃墓所也。想必以三
其间者。制度间或文或质耳。若其祖祢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则乃大体不可变者也。谨之崇之。以为之本。则朱岂变乎周。周岂变乎殷哉。论语集注曰。三纲五常。三代相因之而不变。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过不及之间耳。正谓此也。若以孔,朱损益之故而欲变祖祢纲常。则不亦无伦之甚乎。子谦之所虑诚是。虽然。弟意则有不然者。从吾所当从而已。从家礼其可已乎。丧祭冠昏之常礼。一遵家礼。而家礼所无之礼。如今之国事及意外变礼。则广考仪礼而行之。恐为得也。且仪礼经文但有为母杖期云。而无练,祥,禫之说。此说出于礼记之杂记也。仪礼疏引之云云。大槩十三月而祥。则主入于庙。而撤去朝夕上食等凡事生之礼乎。此则不可知也。若以朱子心丧之意推之。则撤去事生之礼。极为未安。若不去此。则荐此祥事云者。乃虚言也。朱子谓主复于寝。事以事生。乃丧中之凶礼也云。时方行此而祝曰。奄及大祥云。则是非欺神之辞乎。礼文残缺。师道不传。凡丧三年之内。事以事生之礼。朱子艰难究得而论辨之。况杖期十三月大祥后心丧曲折规例。似必难考于传记。不知何以处之。子贡心丧。反筑室于场。场乃墓所也。想必以三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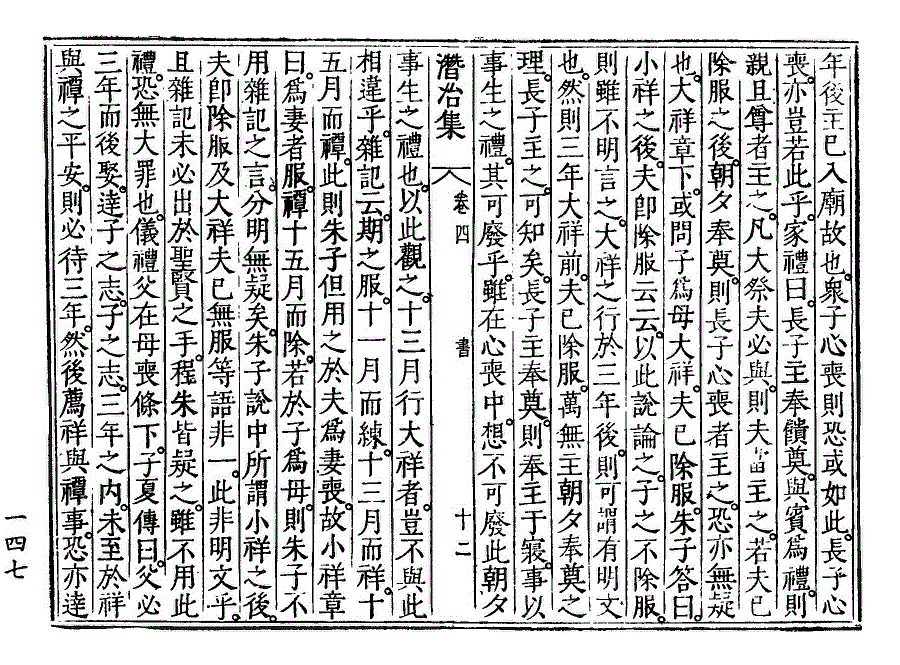 年后主已入庙故也。众子心丧则恐或如此。长子心丧。亦岂若此乎。家礼曰。长子主奉馈奠。与宾为礼。则亲且尊者主之。凡大祭夫必与。则夫当主之。若夫已除服之后。朝夕奉奠。则长子心丧者主之。恐亦无疑也。大祥章下。或问子为母大祥。夫已除服。朱子答曰。小祥之后。夫即除服云云。以此说论之。子之不除服。则虽不明言之。大祥之行于三年后。则可谓有明文也。然则三年大祥前。夫已除服。万无主朝夕奉奠之理。长子主之。可知矣。长子主奉奠。则奉主于寝。事以事生之礼。其可废乎。虽在心丧中。想不可废此朝夕事生之礼也。以此观之。十三月行大祥者。岂不与此相违乎。杂记云。期之服。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则朱子但用之于夫为妻丧。故小祥章曰。为妻者服。禫十五月而除。若于子为母。则朱子不用杂记之言。分明无疑矣。朱子说中所谓小祥之后。夫即除服及大祥夫已无服等语非一。此非明文乎。且杂记未必出于圣贤之手。程朱皆疑之。虽不用此礼。恐无大罪也。仪礼父在母丧条下。子夏传曰。父必三年而后娶。达子之志。子之志。三年之内。未至于祥与禫之平安。则必待三年。然后荐祥与禫事。恐亦达
年后主已入庙故也。众子心丧则恐或如此。长子心丧。亦岂若此乎。家礼曰。长子主奉馈奠。与宾为礼。则亲且尊者主之。凡大祭夫必与。则夫当主之。若夫已除服之后。朝夕奉奠。则长子心丧者主之。恐亦无疑也。大祥章下。或问子为母大祥。夫已除服。朱子答曰。小祥之后。夫即除服云云。以此说论之。子之不除服。则虽不明言之。大祥之行于三年后。则可谓有明文也。然则三年大祥前。夫已除服。万无主朝夕奉奠之理。长子主之。可知矣。长子主奉奠。则奉主于寝。事以事生之礼。其可废乎。虽在心丧中。想不可废此朝夕事生之礼也。以此观之。十三月行大祥者。岂不与此相违乎。杂记云。期之服。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则朱子但用之于夫为妻丧。故小祥章曰。为妻者服。禫十五月而除。若于子为母。则朱子不用杂记之言。分明无疑矣。朱子说中所谓小祥之后。夫即除服及大祥夫已无服等语非一。此非明文乎。且杂记未必出于圣贤之手。程朱皆疑之。虽不用此礼。恐无大罪也。仪礼父在母丧条下。子夏传曰。父必三年而后娶。达子之志。子之志。三年之内。未至于祥与禫之平安。则必待三年。然后荐祥与禫事。恐亦达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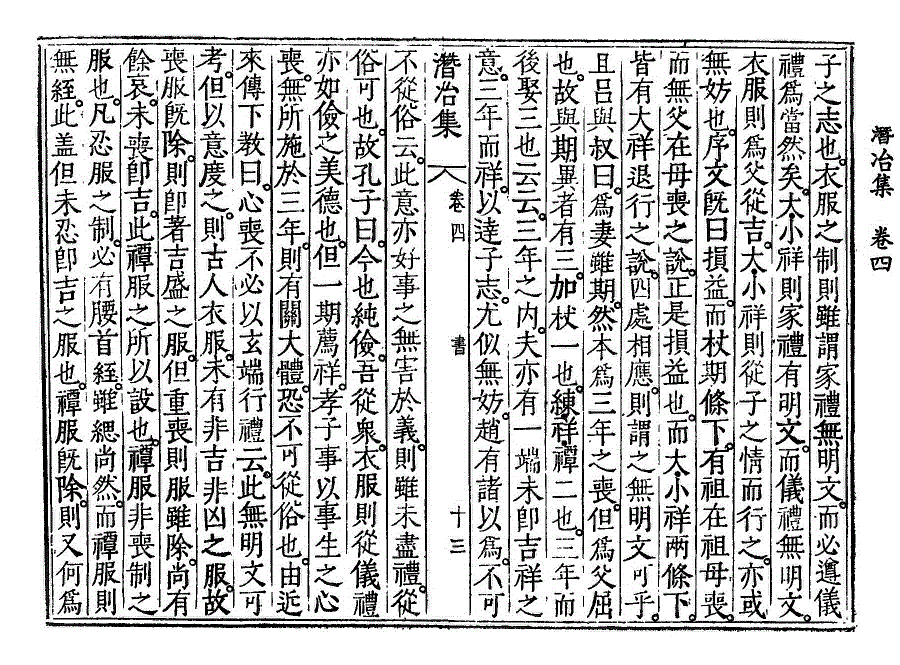 子之志也。衣服之制则虽谓家礼无明文。而必遵仪礼为当然矣。大,小祥则家礼有明文。而仪礼无明文。衣服则为父从吉。大,小祥则从子之情而行之。亦或无妨也。序文既曰损益。而杖期条下。有祖在祖母丧。而无父在母丧之说。正是损益也。而大,小祥两条下。皆有大祥退行之说。四处相应。则谓之无明文可乎。且吕与叔曰。为妻虽期。然本为三年之丧。但为父屈也。故与期异者有三。加杖一也。练,祥,禫二也。三年而后娶三也云云。三年之内。夫亦有一端未即吉祥之意。三年而祥。以达子志。尤似无妨。赵有诸以为。不可不从俗云。此意亦好事之无害于义。则虽未尽礼。从俗可也。故孔子曰。今也纯俭。吾从众。衣服则从仪礼亦如俭之美德也。但一期荐祥。孝子事以事生之心丧。无所施于三年。则有关大体。恐不可从俗也。由近来传下教曰。心丧不必以玄端行礼云。此无明文可考。但以意度之。则古人衣服。未有非吉非凶之服。故丧服既除。则即著吉盛之服。但重丧则服虽除。尚有馀哀。未丧即吉。此禫服之所以设也。禫服非丧制之服也。凡忍服之制。必有腰首绖。虽缌尚然。而禫服则无绖。此盖但未忍即吉之服也。禫服既除。则又何为
子之志也。衣服之制则虽谓家礼无明文。而必遵仪礼为当然矣。大,小祥则家礼有明文。而仪礼无明文。衣服则为父从吉。大,小祥则从子之情而行之。亦或无妨也。序文既曰损益。而杖期条下。有祖在祖母丧。而无父在母丧之说。正是损益也。而大,小祥两条下。皆有大祥退行之说。四处相应。则谓之无明文可乎。且吕与叔曰。为妻虽期。然本为三年之丧。但为父屈也。故与期异者有三。加杖一也。练,祥,禫二也。三年而后娶三也云云。三年之内。夫亦有一端未即吉祥之意。三年而祥。以达子志。尤似无妨。赵有诸以为。不可不从俗云。此意亦好事之无害于义。则虽未尽礼。从俗可也。故孔子曰。今也纯俭。吾从众。衣服则从仪礼亦如俭之美德也。但一期荐祥。孝子事以事生之心丧。无所施于三年。则有关大体。恐不可从俗也。由近来传下教曰。心丧不必以玄端行礼云。此无明文可考。但以意度之。则古人衣服。未有非吉非凶之服。故丧服既除。则即著吉盛之服。但重丧则服虽除。尚有馀哀。未丧即吉。此禫服之所以设也。禫服非丧制之服也。凡忍服之制。必有腰首绖。虽缌尚然。而禫服则无绖。此盖但未忍即吉之服也。禫服既除。则又何为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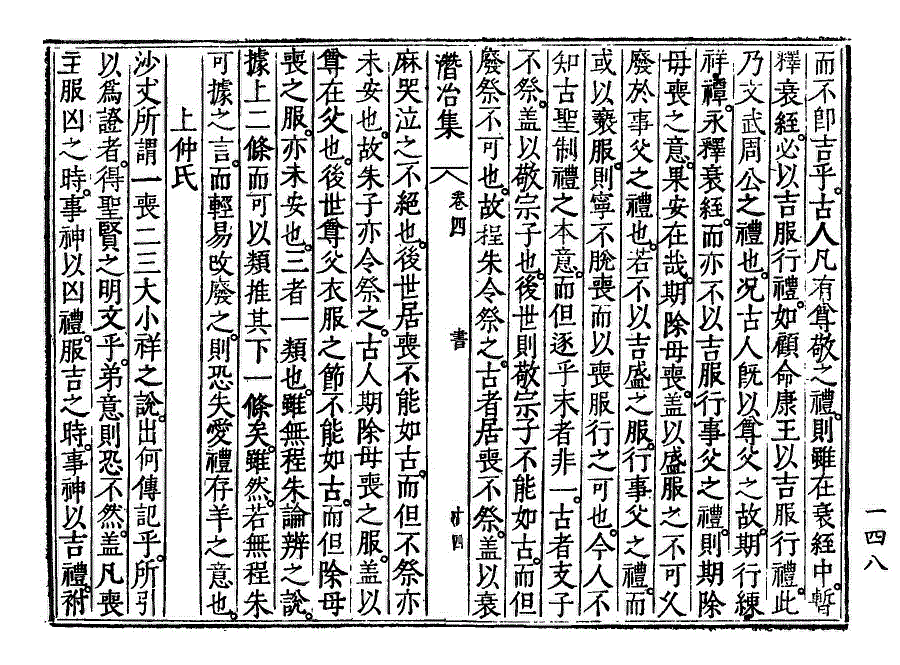 而不即吉乎。古人凡有尊敬之礼。则虽在衰绖中。暂释衰绖。必以吉服行礼。如顾命康王以吉服行礼。此乃文武周公之礼也。况古人既以尊父之故。期行练,祥,禫。永释衰绖。而亦不以吉服行事父之礼。则期除母丧之意。果安在哉。期除母丧。盖以盛服之不可久废于事父之礼也。若不以吉盛之服。行事父之礼。而或以亵服。则宁不脱丧而以丧服行之可也。今人不知古圣制礼之本意。而但逐乎末者非一。古者支子不祭。盖以敬宗子也。后世则敬宗子不能如古。而但废祭不可也。故程朱令祭之。古者居丧不祭。盖以衰麻哭泣之不绝也。后世居丧不能如古。而但不祭亦未安也。故朱子亦令祭之。古人期除母丧之服。盖以尊在父也。后世尊父衣服之节不能如古。而但除母丧之服。亦未安也。三者一类也。虽无程朱论辨之说。据上二条而可以类推其下一条矣。虽然。若无程朱可据之言。而轻易改废之。则恐失爱礼存羊之意也。
而不即吉乎。古人凡有尊敬之礼。则虽在衰绖中。暂释衰绖。必以吉服行礼。如顾命康王以吉服行礼。此乃文武周公之礼也。况古人既以尊父之故。期行练,祥,禫。永释衰绖。而亦不以吉服行事父之礼。则期除母丧之意。果安在哉。期除母丧。盖以盛服之不可久废于事父之礼也。若不以吉盛之服。行事父之礼。而或以亵服。则宁不脱丧而以丧服行之可也。今人不知古圣制礼之本意。而但逐乎末者非一。古者支子不祭。盖以敬宗子也。后世则敬宗子不能如古。而但废祭不可也。故程朱令祭之。古者居丧不祭。盖以衰麻哭泣之不绝也。后世居丧不能如古。而但不祭亦未安也。故朱子亦令祭之。古人期除母丧之服。盖以尊在父也。后世尊父衣服之节不能如古。而但除母丧之服。亦未安也。三者一类也。虽无程朱论辨之说。据上二条而可以类推其下一条矣。虽然。若无程朱可据之言。而轻易改废之。则恐失爱礼存羊之意也。上仲氏
沙丈所谓一丧二三大小祥之说。出何传记乎。所引以为證者。得圣贤之明文乎。弟意则恐不然。盖凡丧主服凶之时。事神以凶礼。服吉之时。事神以吉礼。祔
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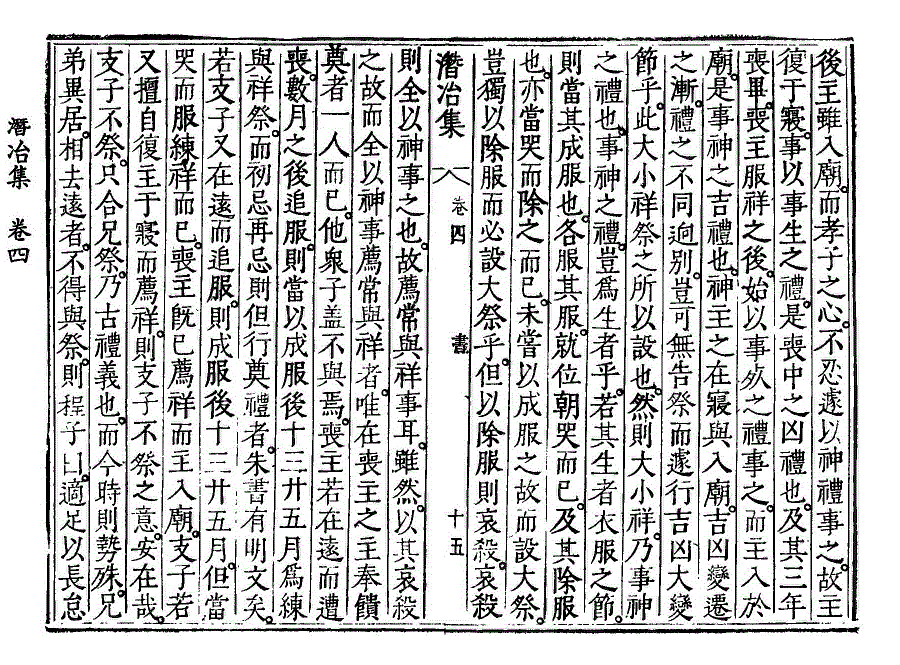 后主虽入庙。而孝子之心。不忍遽以神礼事之。故主复于寝。事以事生之礼。是丧中之凶礼也。及其三年丧毕。丧主服祥之后。始以事死之礼事之。而主入于庙。是事神之吉礼也。神主之在寝与入庙。吉凶变迁之渐。礼之不同迥别。岂可无告祭而遽行吉凶大变节乎。此大小祥祭之所以设也。然则大小祥。乃事神之礼也。事神之礼。岂为生者乎。若其生者衣服之节。则当其成服也。各服其服。就位朝哭而已。及其除服也。亦当哭而除之而已。未尝以成服之故而设大祭。岂独以除服而必设大祭乎。但以除服则哀杀。哀杀则全以神事之也。故荐常与祥事耳。虽然以其哀杀之故而全以神事荐常与祥者。唯在丧主之主奉馈奠者一人而已。他众子盖不与焉。丧主若在远而遭丧。数月之后追服。则当以成服后十三廿五月为练与祥祭。而初忌再忌则但行奠礼者。朱书有明文矣。若支子又在远而追服。则成服后十三廿五月。但当哭而服练,祥而已。丧主既已荐祥而主入庙。支子若又擅自于复主寝而荐祥。则支子不祭之意。安在哉。支子不祭。只合兄祭。乃古礼义也。而今时则势殊。兄弟异居。相去远者。不得与祭。则程子曰。适足以长怠
后主虽入庙。而孝子之心。不忍遽以神礼事之。故主复于寝。事以事生之礼。是丧中之凶礼也。及其三年丧毕。丧主服祥之后。始以事死之礼事之。而主入于庙。是事神之吉礼也。神主之在寝与入庙。吉凶变迁之渐。礼之不同迥别。岂可无告祭而遽行吉凶大变节乎。此大小祥祭之所以设也。然则大小祥。乃事神之礼也。事神之礼。岂为生者乎。若其生者衣服之节。则当其成服也。各服其服。就位朝哭而已。及其除服也。亦当哭而除之而已。未尝以成服之故而设大祭。岂独以除服而必设大祭乎。但以除服则哀杀。哀杀则全以神事之也。故荐常与祥事耳。虽然以其哀杀之故而全以神事荐常与祥者。唯在丧主之主奉馈奠者一人而已。他众子盖不与焉。丧主若在远而遭丧。数月之后追服。则当以成服后十三廿五月为练与祥祭。而初忌再忌则但行奠礼者。朱书有明文矣。若支子又在远而追服。则成服后十三廿五月。但当哭而服练,祥而已。丧主既已荐祥而主入庙。支子若又擅自于复主寝而荐祥。则支子不祭之意。安在哉。支子不祭。只合兄祭。乃古礼义也。而今时则势殊。兄弟异居。相去远者。不得与祭。则程子曰。适足以长怠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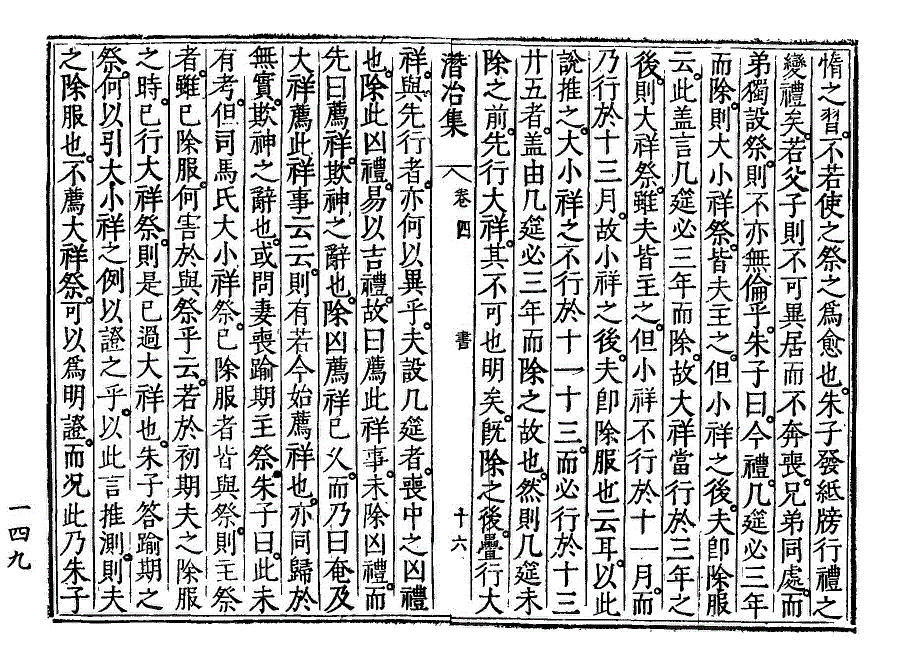 惰之习。不若使之祭之为愈也。朱子发纸榜行礼之变礼矣。若父子则不可异居而不奔丧。兄弟同处。而弟独设祭。则不亦无伦乎。朱子曰。今礼。几筵必三年而除。则大小祥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后。夫即除服云。此盖言几筵必三年而除。故大祥当行于三年之后。则大祥祭。虽夫皆主之。但小祥不行于十一月。而乃行于十三月。故小祥之后。夫即除服也云耳。以此说推之。大小祥之不行于十一十三。而必行于十三廿五者。盖由几筵必三年而除之故也。然则几筵未除之前。先行大祥。其不可也明矣。既除之后。叠行大祥。与先行者。亦何以异乎。夫设几筵者。丧中之凶礼也。除此凶礼。易以吉礼。故曰荐此祥事。未除凶礼。而先曰荐祥。欺神之辞也。除凶荐祥已久。而乃曰奄及大祥荐此祥事云云。则有若今始荐祥也。亦同归于无实。欺神之辞也。或问妻丧踰期主祭。朱子曰。此未有考。但司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与祭。则主祭者。虽已除服。何害于与祭乎云。若于初期夫之除服之时。已行大祥祭。则是已过大祥也。朱子答踰期之祭。何以引大,小祥之例以證之乎。以此言推测。则夫之除服也。不荐大祥祭。可以为明證。而况此乃朱子
惰之习。不若使之祭之为愈也。朱子发纸榜行礼之变礼矣。若父子则不可异居而不奔丧。兄弟同处。而弟独设祭。则不亦无伦乎。朱子曰。今礼。几筵必三年而除。则大小祥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后。夫即除服云。此盖言几筵必三年而除。故大祥当行于三年之后。则大祥祭。虽夫皆主之。但小祥不行于十一月。而乃行于十三月。故小祥之后。夫即除服也云耳。以此说推之。大小祥之不行于十一十三。而必行于十三廿五者。盖由几筵必三年而除之故也。然则几筵未除之前。先行大祥。其不可也明矣。既除之后。叠行大祥。与先行者。亦何以异乎。夫设几筵者。丧中之凶礼也。除此凶礼。易以吉礼。故曰荐此祥事。未除凶礼。而先曰荐祥。欺神之辞也。除凶荐祥已久。而乃曰奄及大祥荐此祥事云云。则有若今始荐祥也。亦同归于无实。欺神之辞也。或问妻丧踰期主祭。朱子曰。此未有考。但司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与祭。则主祭者。虽已除服。何害于与祭乎云。若于初期夫之除服之时。已行大祥祭。则是已过大祥也。朱子答踰期之祭。何以引大,小祥之例以證之乎。以此言推测。则夫之除服也。不荐大祥祭。可以为明證。而况此乃朱子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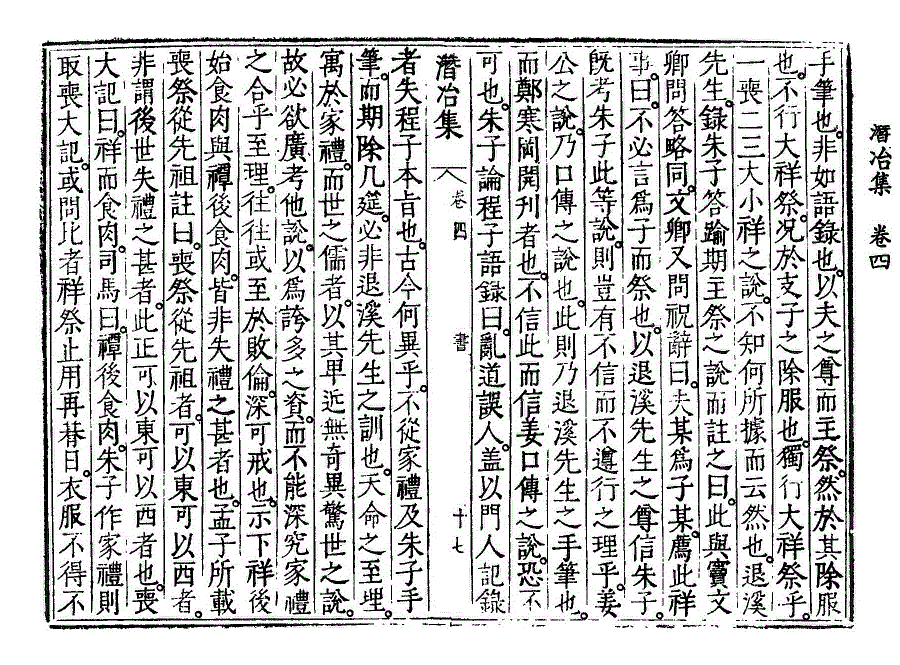 手笔也。非如语录也。以夫之尊而主祭。然于其除服也。不行大祥祭。况于支子之除服也。独行大祥祭乎。一丧二三大小祥之说。不知何所据而云然也。退溪先生。录朱子答踰期主祭之说而注之曰。此与窦文卿问答略同。文卿又问祝辞曰。夫某为子某。荐此祥事。曰。不必言为子而祭也。以退溪先生之尊信朱子。既考朱子此等说。则岂有不信而不遵行之理乎。姜公之说。乃口传之说也。此则乃退溪先生之手笔也。而郑寒冈开刊者也。不信此而信姜口传之说。恐不可也。朱子论程子语录曰。乱道误人。盖以门人记录者失程子本旨也。古今何异乎。不从家礼及朱子手笔。而期除几筵。必非退溪先生之训也。天命之至理。寓于家礼。而世之儒者。以其卑近无奇异惊世之说。故必欲广考他说。以为誇多之资。而不能深究家礼之合乎至理。往往或至于败伦。深可戒也。示下祥后始食肉与禫后食肉。皆非失礼之甚者也。孟子所载丧祭从先祖注曰。丧祭从先祖者。可以东可以西者。非谓后世失礼之甚者。此正可以东可以西者也。丧大记曰。祥而食肉。司马曰。禫后食肉。朱子作家礼则取丧大记。或问比者祥祭止用再期日。衣服不得不
手笔也。非如语录也。以夫之尊而主祭。然于其除服也。不行大祥祭。况于支子之除服也。独行大祥祭乎。一丧二三大小祥之说。不知何所据而云然也。退溪先生。录朱子答踰期主祭之说而注之曰。此与窦文卿问答略同。文卿又问祝辞曰。夫某为子某。荐此祥事。曰。不必言为子而祭也。以退溪先生之尊信朱子。既考朱子此等说。则岂有不信而不遵行之理乎。姜公之说。乃口传之说也。此则乃退溪先生之手笔也。而郑寒冈开刊者也。不信此而信姜口传之说。恐不可也。朱子论程子语录曰。乱道误人。盖以门人记录者失程子本旨也。古今何异乎。不从家礼及朱子手笔。而期除几筵。必非退溪先生之训也。天命之至理。寓于家礼。而世之儒者。以其卑近无奇异惊世之说。故必欲广考他说。以为誇多之资。而不能深究家礼之合乎至理。往往或至于败伦。深可戒也。示下祥后始食肉与禫后食肉。皆非失礼之甚者也。孟子所载丧祭从先祖注曰。丧祭从先祖者。可以东可以西者。非谓后世失礼之甚者。此正可以东可以西者也。丧大记曰。祥而食肉。司马曰。禫后食肉。朱子作家礼则取丧大记。或问比者祥祭止用再期日。衣服不得不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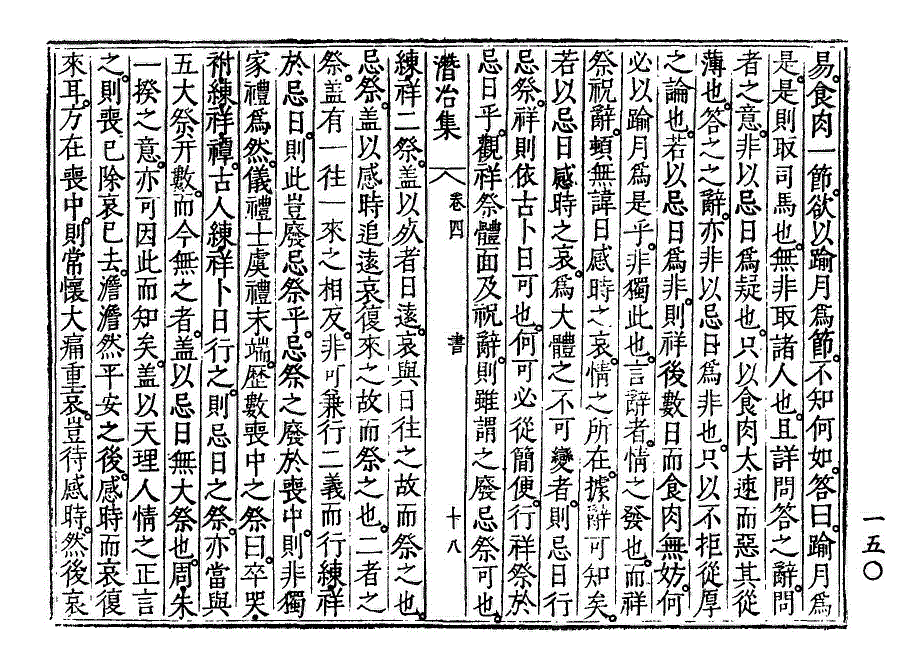 易。食肉一节。欲以踰月为节。不知何如。答曰。踰月为是。是则取司马也。无非取诸人也。且详问答之辞。问者之意。非以忌日为疑也。只以食肉太速而恶其从薄也。答之之辞。亦非以忌日为非也。只以不拒从厚之论也。若以忌日为非。则祥后数日而食肉无妨。何必以踰月为是乎。非独此也。言辞者。情之发也。而祥祭祝辞。顿无讳日感时之哀。情之所在。据辞可知矣。若以忌日感时之哀。为大体之不可变者。则忌日行忌祭。祥则依古卜日可也。何可必从简便。行祥祭于忌日乎。观祥祭体面及祝辞。则虽谓之废忌祭可也。练,祥二祭。盖以死者日远。哀与日往之故而祭之也。忌祭。盖以感时追远哀复来之故而祭之也。二者之祭。盖有一往一来之相反。非可兼行二义而行练,祥于忌日。则此岂废忌祭乎。忌祭之废于丧中。则非独家礼为然。仪礼士虞礼末端。历数丧中之祭曰。卒哭,祔,练,祥,禫。古人练,祥卜日行之。则忌日之祭。亦当与五大祭并数。而今无之者。盖以忌日无大祭也。周,朱一揆之意。亦可因此而知矣。盖以天理人情之正言之。则丧已除哀已去。澹澹然平安之后。感时而哀复来耳。方在丧中。则常怀大痛重哀岂待感时。然后哀
易。食肉一节。欲以踰月为节。不知何如。答曰。踰月为是。是则取司马也。无非取诸人也。且详问答之辞。问者之意。非以忌日为疑也。只以食肉太速而恶其从薄也。答之之辞。亦非以忌日为非也。只以不拒从厚之论也。若以忌日为非。则祥后数日而食肉无妨。何必以踰月为是乎。非独此也。言辞者。情之发也。而祥祭祝辞。顿无讳日感时之哀。情之所在。据辞可知矣。若以忌日感时之哀。为大体之不可变者。则忌日行忌祭。祥则依古卜日可也。何可必从简便。行祥祭于忌日乎。观祥祭体面及祝辞。则虽谓之废忌祭可也。练,祥二祭。盖以死者日远。哀与日往之故而祭之也。忌祭。盖以感时追远哀复来之故而祭之也。二者之祭。盖有一往一来之相反。非可兼行二义而行练,祥于忌日。则此岂废忌祭乎。忌祭之废于丧中。则非独家礼为然。仪礼士虞礼末端。历数丧中之祭曰。卒哭,祔,练,祥,禫。古人练,祥卜日行之。则忌日之祭。亦当与五大祭并数。而今无之者。盖以忌日无大祭也。周,朱一揆之意。亦可因此而知矣。盖以天理人情之正言之。则丧已除哀已去。澹澹然平安之后。感时而哀复来耳。方在丧中。则常怀大痛重哀岂待感时。然后哀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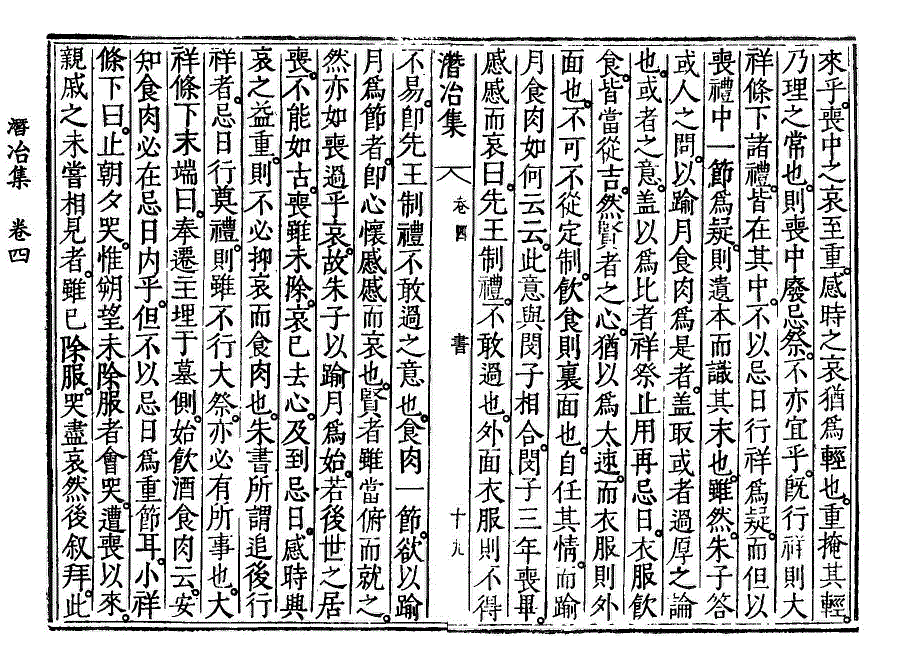 来乎。丧中之哀至重。感时之哀犹为轻也。重掩其轻。乃理之常也。则丧中废忌祭。不亦宜乎。既行祥则大祥条下诸礼。皆在其中。不以忌日行祥为疑。而但以丧礼中一节为疑。则遗本而识其末也。虽然。朱子答或人之问。以踰月食肉为是者。盖取或者过厚之论也。或者之意。盖以为比者祥祭止用再忌日。衣服饮食。皆当从吉。然贤者之心。犹以为太速。而衣服则外面也。不可不从定制。饮食则里面也。自任其情。而踰月食肉如何云云。此意与闵子相合。闵子三年丧毕。戚戚而哀曰。先王制礼。不敢过也。外面衣服则不得不易。即先王制礼不敢过之意也。食肉一节。欲以踰月为节者。即心怀戚戚而哀也。贤者虽当俯而就之。然亦如丧过乎哀。故朱子以踰月为始。若后世之居丧。不能如古。丧虽未除。哀已去心。及到忌日。感时兴哀之益重。则不必抑哀而食肉也。朱书所谓追后行祥者。忌日行奠礼。则虽不行大祭。亦必有所事也。大祥条下末端曰。奉迁主埋于墓侧。始饮酒食肉云。安知食肉必在忌日内乎。但不以忌日为重节耳。小祥条下曰。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会哭。遭丧以来。亲戚之未尝相见者。虽已除服。哭尽哀然后叙拜。此
来乎。丧中之哀至重。感时之哀犹为轻也。重掩其轻。乃理之常也。则丧中废忌祭。不亦宜乎。既行祥则大祥条下诸礼。皆在其中。不以忌日行祥为疑。而但以丧礼中一节为疑。则遗本而识其末也。虽然。朱子答或人之问。以踰月食肉为是者。盖取或者过厚之论也。或者之意。盖以为比者祥祭止用再忌日。衣服饮食。皆当从吉。然贤者之心。犹以为太速。而衣服则外面也。不可不从定制。饮食则里面也。自任其情。而踰月食肉如何云云。此意与闵子相合。闵子三年丧毕。戚戚而哀曰。先王制礼。不敢过也。外面衣服则不得不易。即先王制礼不敢过之意也。食肉一节。欲以踰月为节者。即心怀戚戚而哀也。贤者虽当俯而就之。然亦如丧过乎哀。故朱子以踰月为始。若后世之居丧。不能如古。丧虽未除。哀已去心。及到忌日。感时兴哀之益重。则不必抑哀而食肉也。朱书所谓追后行祥者。忌日行奠礼。则虽不行大祭。亦必有所事也。大祥条下末端曰。奉迁主埋于墓侧。始饮酒食肉云。安知食肉必在忌日内乎。但不以忌日为重节耳。小祥条下曰。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会哭。遭丧以来。亲戚之未尝相见者。虽已除服。哭尽哀然后叙拜。此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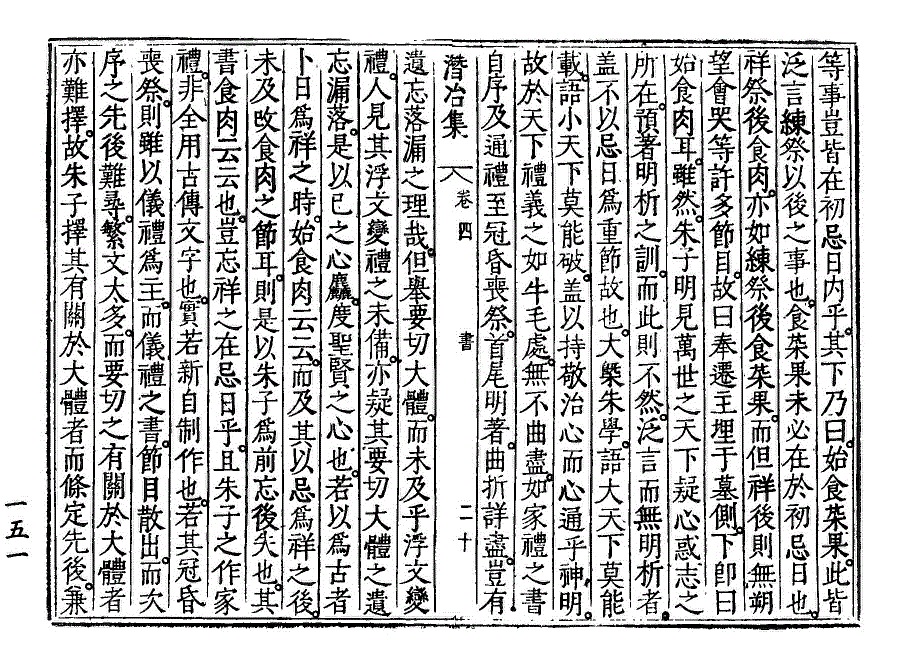 等事岂皆在初忌日内乎。其下乃曰。始食菜果。此皆泛言练祭以后之事也。食菜果未必在于初忌日也。祥祭后食肉。亦如练祭后食菜果。而但祥后则无朔望会哭等许多节目。故曰奉迁主埋于墓侧。下即曰始食肉耳。虽然。朱子明见万世之天下疑心惑志之所在。预著明析之训。而此则不然。泛言而无明析者。盖不以忌日为重节故也。大槩朱学。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盖以持敬治心而心通乎神明。故于天下礼义之如牛毛处无不曲尽。如家礼之书自序及通礼至冠昏丧祭。首尾明著。曲折详尽。岂有遗忘落漏之理哉。但举要切大体。而未及乎浮文变礼。人见其浮文变礼之未备。亦疑其要切大体之遗忘漏落。是以己之心粗。度圣贤之心也。若以为古者卜日为祥之时。始食肉云云。而及其以忌为祥之后。未及改食肉之节耳。则是以朱子为前忘后失也。其书食肉云云也。岂忘祥之在忌日乎。且朱子之作家礼。非全用古传文字也。实若新自制作也。若其冠昏丧祭。则虽以仪礼为主。而仪礼之书。节目散出。而次序之先后难寻。繁文太多。而要切之有关于大体者亦难择。故朱子择其有关于大体者而条定先后。兼
等事岂皆在初忌日内乎。其下乃曰。始食菜果。此皆泛言练祭以后之事也。食菜果未必在于初忌日也。祥祭后食肉。亦如练祭后食菜果。而但祥后则无朔望会哭等许多节目。故曰奉迁主埋于墓侧。下即曰始食肉耳。虽然。朱子明见万世之天下疑心惑志之所在。预著明析之训。而此则不然。泛言而无明析者。盖不以忌日为重节故也。大槩朱学。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盖以持敬治心而心通乎神明。故于天下礼义之如牛毛处无不曲尽。如家礼之书自序及通礼至冠昏丧祭。首尾明著。曲折详尽。岂有遗忘落漏之理哉。但举要切大体。而未及乎浮文变礼。人见其浮文变礼之未备。亦疑其要切大体之遗忘漏落。是以己之心粗。度圣贤之心也。若以为古者卜日为祥之时。始食肉云云。而及其以忌为祥之后。未及改食肉之节耳。则是以朱子为前忘后失也。其书食肉云云也。岂忘祥之在忌日乎。且朱子之作家礼。非全用古传文字也。实若新自制作也。若其冠昏丧祭。则虽以仪礼为主。而仪礼之书。节目散出。而次序之先后难寻。繁文太多。而要切之有关于大体者亦难择。故朱子择其有关于大体者而条定先后。兼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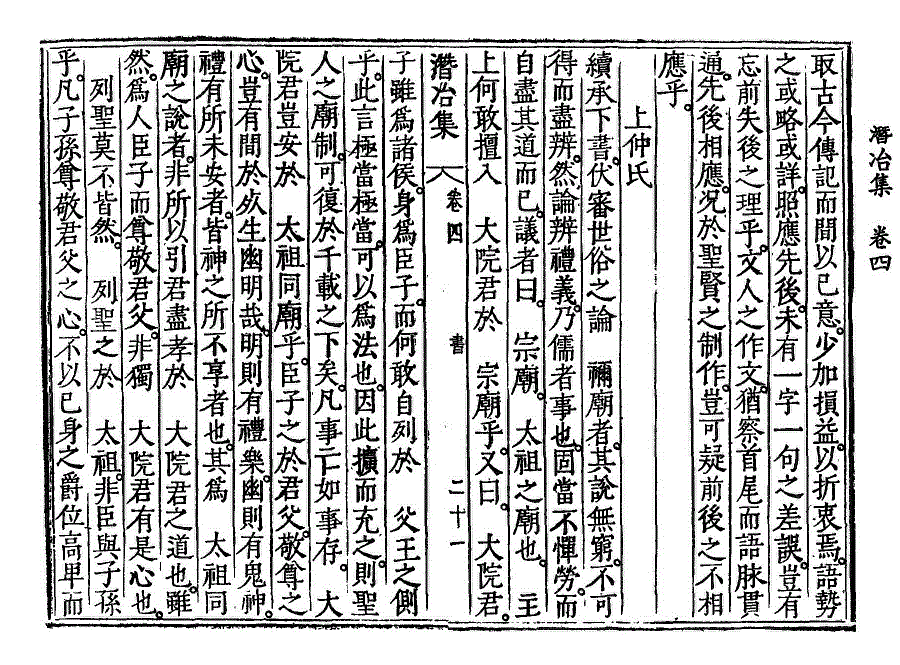 取古今传记而间以己意。少加损益。以折衷焉。语势之或略或详。照应先后。未有一字一句之差误。岂有忘前失后之理乎。文人之作文。犹察首尾而语脉贯通。先后相应。况于圣贤之制作。岂可疑前后之不相应乎。
取古今传记而间以己意。少加损益。以折衷焉。语势之或略或详。照应先后。未有一字一句之差误。岂有忘前失后之理乎。文人之作文。犹察首尾而语脉贯通。先后相应。况于圣贤之制作。岂可疑前后之不相应乎。上仲氏
续承下书。伏审世俗之论 祢庙者。其说无穷。不可得而尽辨。然论辨礼义。乃儒者事也。固当不惮劳。而自尽其道而已。议者曰。 宗庙。 太祖之庙也。 主上何敢擅入 大院君于 宗庙乎。又曰。 大院君。子虽为诸侯。身为臣子。而何敢自列于 父王之侧乎。此言极当极当。可以为法也。因此扩而充之。则圣人之庙制。可复于千载之下矣。凡事亡如事存。 大院君岂安于 太祖同庙乎。臣子之于君父。敬尊之心。岂有间于死生幽明哉。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礼有所未安者。皆神之所不享者也。其为 太祖同庙之说者。非所以引君尽孝于 大院君之道也。虽然。为人臣子而尊敬君父。非独 大院君有是心也。 列圣莫不皆然。 列圣之于 太祖。非臣与子孙乎。凡子孙尊敬君父之心。不以己身之爵位高卑而
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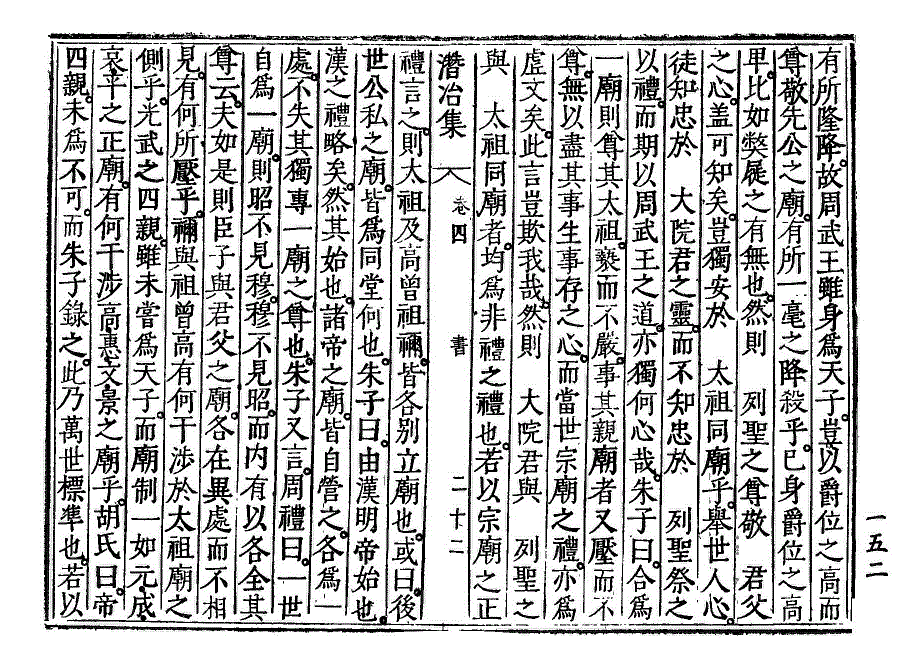 有所隆降。故周武王虽身为天子。岂以爵位之高而尊敬先公之庙。有所一毫之降杀乎。己身爵位之高卑。比如弊屣之有无也。然则 列圣之尊敬 君父之心。盖可知矣。岂独安于 太祖同庙乎。举世人心。徒知忠于 大院君之灵。而不知忠于 列圣祭之以礼。而期以周武王之道。亦独何心哉。朱子曰。合为一庙则尊其太祖。亵而不严。事其亲庙者又压而不尊。无以尽其事生事存之心。而当世宗庙之礼。亦为虚文矣。此言岂欺我哉。然则 大院君与 列圣之与 太祖同庙者。均为非礼之礼也。若以宗庙之正礼言之。则太祖及高曾祖祢。皆各别立庙也。或曰。后世公私之庙。皆为同堂何也。朱子曰。由汉明帝始也。汉之礼略矣。然其始也。诸帝之庙。皆自营之。各为一处。不失其独专一庙之尊也。朱子又言。周礼曰。一世自为一庙。则昭不见穆。穆不见昭。而内有以各全其尊云。夫如是则臣子与君父之庙。各在异处而不相见。有何所压乎。祢与祖曾高有何干涉于太祖庙之侧乎。光武之四亲。虽未尝为天子。而庙制一如元,成,哀,平之正庙。有何干涉高,惠,文,景之庙乎。胡氏曰。帝四亲。未为不可。而朱子录之。此乃万世标准也。若以
有所隆降。故周武王虽身为天子。岂以爵位之高而尊敬先公之庙。有所一毫之降杀乎。己身爵位之高卑。比如弊屣之有无也。然则 列圣之尊敬 君父之心。盖可知矣。岂独安于 太祖同庙乎。举世人心。徒知忠于 大院君之灵。而不知忠于 列圣祭之以礼。而期以周武王之道。亦独何心哉。朱子曰。合为一庙则尊其太祖。亵而不严。事其亲庙者又压而不尊。无以尽其事生事存之心。而当世宗庙之礼。亦为虚文矣。此言岂欺我哉。然则 大院君与 列圣之与 太祖同庙者。均为非礼之礼也。若以宗庙之正礼言之。则太祖及高曾祖祢。皆各别立庙也。或曰。后世公私之庙。皆为同堂何也。朱子曰。由汉明帝始也。汉之礼略矣。然其始也。诸帝之庙。皆自营之。各为一处。不失其独专一庙之尊也。朱子又言。周礼曰。一世自为一庙。则昭不见穆。穆不见昭。而内有以各全其尊云。夫如是则臣子与君父之庙。各在异处而不相见。有何所压乎。祢与祖曾高有何干涉于太祖庙之侧乎。光武之四亲。虽未尝为天子。而庙制一如元,成,哀,平之正庙。有何干涉高,惠,文,景之庙乎。胡氏曰。帝四亲。未为不可。而朱子录之。此乃万世标准也。若以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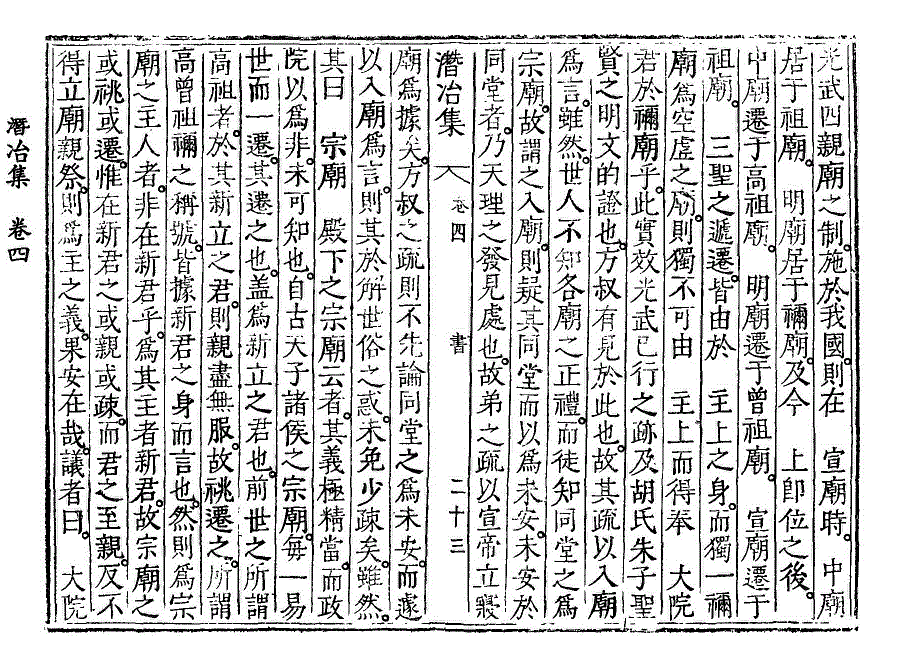 光武四亲庙之制。施于我国。则在 宣庙时。 中庙居于祖庙。 明庙居于祢庙。及今 上即位之后。 中庙迁于高祖庙。 明庙迁于曾祖庙。 宣庙迁于祖庙。 三圣之递迁。皆由于 主上之身。而独一祢庙为空虚之庙。则独不可由 主上而得奉 大院君于祢庙乎。此实效光武已行之迹及胡氏朱子圣贤之明文的證也。方叔有见于此也。故其疏以入庙为言。虽然。世人不知各庙之正礼。而徒知同堂之为宗庙。故谓之入庙。则疑其同堂而以为未安。未安于同堂者。乃天理之发见处也。故弟之疏以宣帝立寝庙为据矣。方叔之疏则不先论同堂之为未安。而遽以入庙为言。则其于解世俗之惑。未免少疏矣。虽然。其曰 宗庙 殿下之宗庙云者。其义极精当。而政院以为非。未可知也。自古天子诸侯之宗庙。每一易世而一迁。其迁之也。盖为新立之君也。前世之所谓高祖者。于其新立之君。则亲尽无服。故祧迁之。所谓高曾祖祢之称号。皆据新君之身而言也。然则为宗庙之主人者。非在新君乎。为其主者新君。故宗庙之或祧或迁。惟在新君之或亲或疏。而君之至亲。反不得立庙亲祭。则为主之义。果安在哉。议者曰。 大院
光武四亲庙之制。施于我国。则在 宣庙时。 中庙居于祖庙。 明庙居于祢庙。及今 上即位之后。 中庙迁于高祖庙。 明庙迁于曾祖庙。 宣庙迁于祖庙。 三圣之递迁。皆由于 主上之身。而独一祢庙为空虚之庙。则独不可由 主上而得奉 大院君于祢庙乎。此实效光武已行之迹及胡氏朱子圣贤之明文的證也。方叔有见于此也。故其疏以入庙为言。虽然。世人不知各庙之正礼。而徒知同堂之为宗庙。故谓之入庙。则疑其同堂而以为未安。未安于同堂者。乃天理之发见处也。故弟之疏以宣帝立寝庙为据矣。方叔之疏则不先论同堂之为未安。而遽以入庙为言。则其于解世俗之惑。未免少疏矣。虽然。其曰 宗庙 殿下之宗庙云者。其义极精当。而政院以为非。未可知也。自古天子诸侯之宗庙。每一易世而一迁。其迁之也。盖为新立之君也。前世之所谓高祖者。于其新立之君。则亲尽无服。故祧迁之。所谓高曾祖祢之称号。皆据新君之身而言也。然则为宗庙之主人者。非在新君乎。为其主者新君。故宗庙之或祧或迁。惟在新君之或亲或疏。而君之至亲。反不得立庙亲祭。则为主之义。果安在哉。议者曰。 大院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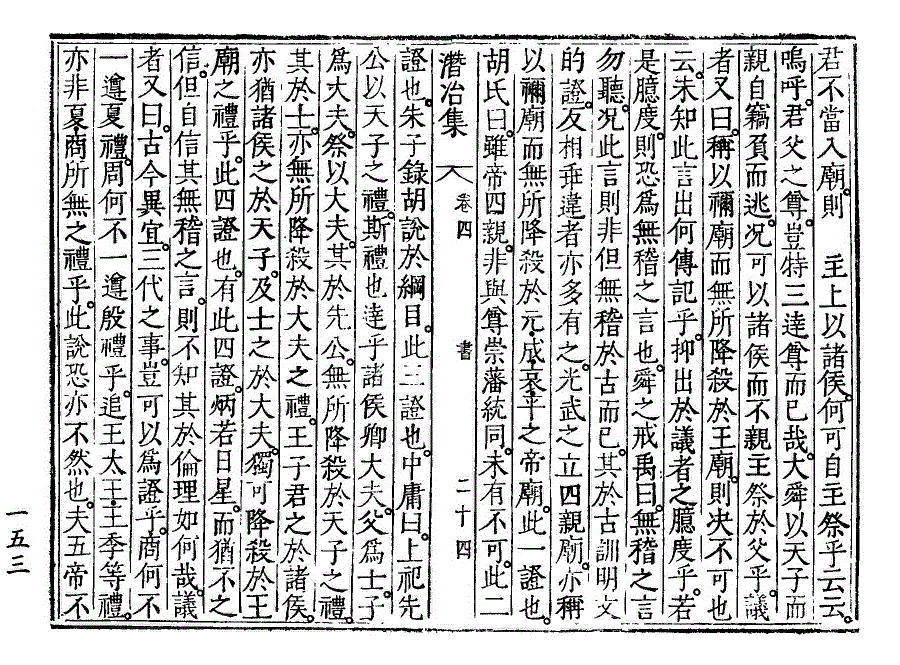 君不当入庙。则 主上以诸侯。何可自主祭乎云云。呜呼。君父之尊。岂特三达尊而已哉。大舜以天子而亲自窃负而逃。况可以诸侯而不亲主祭于父乎。议者又曰。称以祢庙而无所降杀于王庙。则决不可也云。未知此言出何传记乎。抑出于议者之臆度乎。若是臆度。则恐为无稽之言也。舜之戒禹曰。无稽之言勿听。况此言则非但无稽于古而已。其于古训明文的證。反相乖违者亦多有之。光武之立四亲庙。亦称以祢庙而无所降杀于元,成,哀,平之帝庙。此一證也。胡氏曰。虽帝四亲。非与尊崇藩统同。未有不可。此二證也。朱子录胡说于纲目。此三證也。中庸曰。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卿大夫。父为士。子为大夫。祭以大夫。其于先公。无所降杀于天子之礼。其于士。亦无所降杀于大夫之礼。王子君之于诸侯。亦犹诸侯之于天子。及士之于大夫。独可降杀于王庙之礼乎。此四證也。有此四證。炳若日星。而犹不之信。但自信其无稽之言。则不知其于伦理如何哉。议者又曰。古今异宜。三代之事。岂可以为證乎。商何不一遵夏礼。周何不一遵殷礼乎。追王太王,王季等礼。亦非夏,商所无之礼乎。此说恐亦不然也。夫五帝不
君不当入庙。则 主上以诸侯。何可自主祭乎云云。呜呼。君父之尊。岂特三达尊而已哉。大舜以天子而亲自窃负而逃。况可以诸侯而不亲主祭于父乎。议者又曰。称以祢庙而无所降杀于王庙。则决不可也云。未知此言出何传记乎。抑出于议者之臆度乎。若是臆度。则恐为无稽之言也。舜之戒禹曰。无稽之言勿听。况此言则非但无稽于古而已。其于古训明文的證。反相乖违者亦多有之。光武之立四亲庙。亦称以祢庙而无所降杀于元,成,哀,平之帝庙。此一證也。胡氏曰。虽帝四亲。非与尊崇藩统同。未有不可。此二證也。朱子录胡说于纲目。此三證也。中庸曰。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卿大夫。父为士。子为大夫。祭以大夫。其于先公。无所降杀于天子之礼。其于士。亦无所降杀于大夫之礼。王子君之于诸侯。亦犹诸侯之于天子。及士之于大夫。独可降杀于王庙之礼乎。此四證也。有此四證。炳若日星。而犹不之信。但自信其无稽之言。则不知其于伦理如何哉。议者又曰。古今异宜。三代之事。岂可以为證乎。商何不一遵夏礼。周何不一遵殷礼乎。追王太王,王季等礼。亦非夏,商所无之礼乎。此说恐亦不然也。夫五帝不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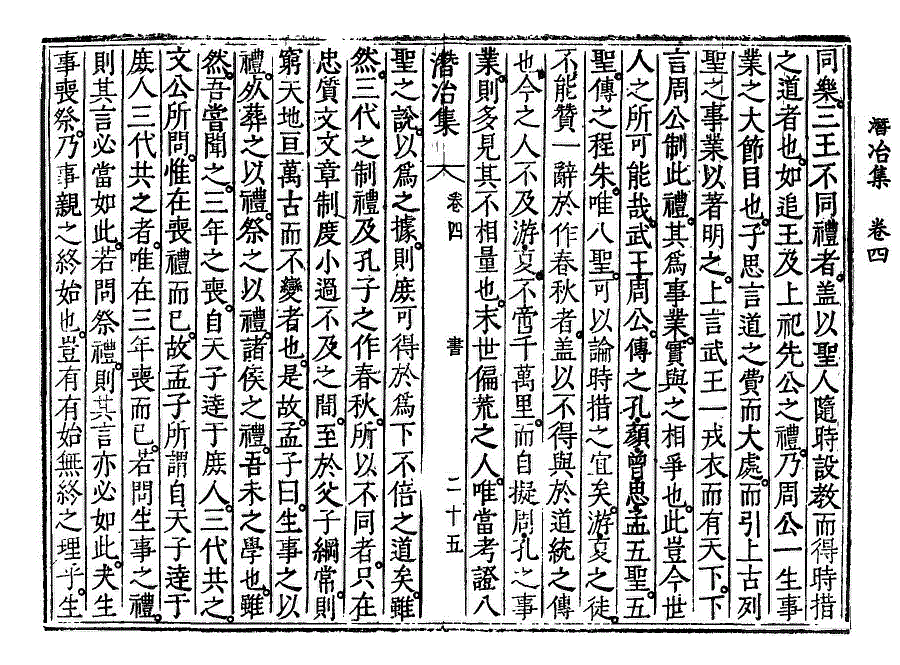 同乐。三王不同礼者。盖以圣人随时设教而得时措之道者也。如追王及上祀先公之礼。乃周公一生事业之大节目也。子思言道之费而大处。而引上古列圣之事业以著明之。上言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下言周公制此礼。其为事业。实与之相争也。此岂今世人之所可能哉。武王,周公。传之孔,颜,曾,思,孟五圣。五圣。传之程朱。唯八圣。可以论时措之宜矣。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于作春秋者。盖以不得与于道统之传也。今之人不及游,夏。不啻千万里。而自拟周,孔之事业。则多见其不相量也。末世偏荒之人。唯当考證八圣之说。以为之据。则庶可得于为下不倍之道矣。虽然。三代之制礼及孔子之作春秋。所以不同者。只在忠质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至于父子纲常。则穷天地亘万古而不变者也。是故。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文公所问。惟在丧礼而已。故孟子所谓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者。唯在三年丧而已。若问生事之礼。则其言必当如此。若问祭礼。则其言亦必如此。夫生事丧祭。乃事亲之终始也。岂有有始无终之理乎。生
同乐。三王不同礼者。盖以圣人随时设教而得时措之道者也。如追王及上祀先公之礼。乃周公一生事业之大节目也。子思言道之费而大处。而引上古列圣之事业以著明之。上言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下言周公制此礼。其为事业。实与之相争也。此岂今世人之所可能哉。武王,周公。传之孔,颜,曾,思,孟五圣。五圣。传之程朱。唯八圣。可以论时措之宜矣。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于作春秋者。盖以不得与于道统之传也。今之人不及游,夏。不啻千万里。而自拟周,孔之事业。则多见其不相量也。末世偏荒之人。唯当考證八圣之说。以为之据。则庶可得于为下不倍之道矣。虽然。三代之制礼及孔子之作春秋。所以不同者。只在忠质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至于父子纲常。则穷天地亘万古而不变者也。是故。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文公所问。惟在丧礼而已。故孟子所谓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者。唯在三年丧而已。若问生事之礼。则其言必当如此。若问祭礼。则其言亦必如此。夫生事丧祭。乃事亲之终始也。岂有有始无终之理乎。生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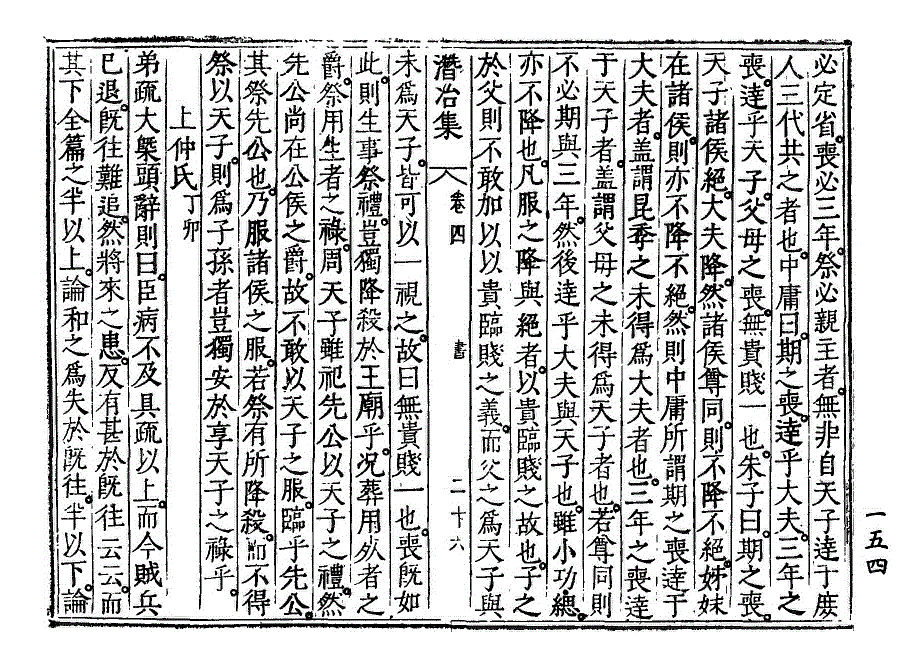 必定省。丧必三年。祭必亲主者。无非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者也。中庸曰。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朱子曰。期之丧。天子诸侯绝。大夫降。然诸侯尊同。则不降不绝。姊妹在诸侯。则亦不降不绝。然则中庸所谓期之丧达于大夫者。盖谓昆季之未得为大夫者也。三年之丧达于天子者。盖谓父母之未得为天子者也。若尊同则不必期与三年。然后达乎大夫与天子也。虽小功,缌。亦不降也。凡服之降与绝者。以贵临贱之故也。子之于父则不敢加以以贵临贱之义。而父之为天子与未为天子。皆可以一视之。故曰无贵贱一也。丧既如此。则生事祭礼。岂独降杀于王庙乎。况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禄。周天子虽祀先公以天子之礼。然先公尚在公侯之爵。故不敢以天子之服。临乎先公。其祭先公也。乃服诸侯之服。若祭有所降杀。而不得祭以天子。则为子孙者岂独安于享天子之禄乎。
必定省。丧必三年。祭必亲主者。无非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者也。中庸曰。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朱子曰。期之丧。天子诸侯绝。大夫降。然诸侯尊同。则不降不绝。姊妹在诸侯。则亦不降不绝。然则中庸所谓期之丧达于大夫者。盖谓昆季之未得为大夫者也。三年之丧达于天子者。盖谓父母之未得为天子者也。若尊同则不必期与三年。然后达乎大夫与天子也。虽小功,缌。亦不降也。凡服之降与绝者。以贵临贱之故也。子之于父则不敢加以以贵临贱之义。而父之为天子与未为天子。皆可以一视之。故曰无贵贱一也。丧既如此。则生事祭礼。岂独降杀于王庙乎。况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禄。周天子虽祀先公以天子之礼。然先公尚在公侯之爵。故不敢以天子之服。临乎先公。其祭先公也。乃服诸侯之服。若祭有所降杀。而不得祭以天子。则为子孙者岂独安于享天子之禄乎。上仲氏(丁卯)
弟疏大槩头辞则曰。臣病不及具疏以上。而今贼兵已退。既往难追。然将来之患。反有甚于既往云云。而其下全篇之半以上。论和之为失于既往。半以下。论
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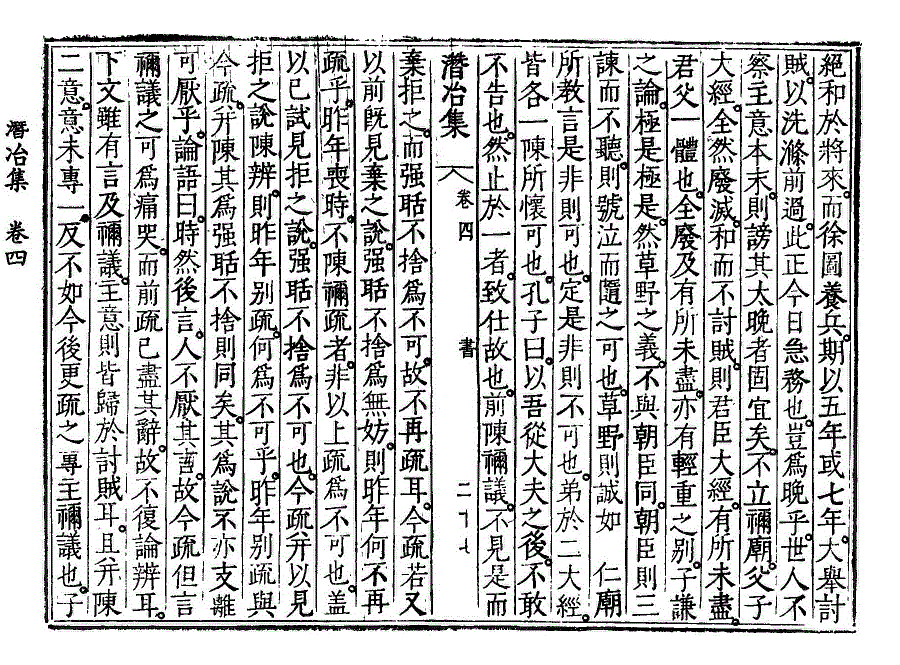 绝和于将来。而徐图养兵。期以五年或七年。大举讨贼。以洗涤前过。此正今日急务也。岂为晚乎。世人不察主意本末。则谤其太晚者固宜矣。不立祢庙。父子大经。全然废灭。和而不讨贼。则君臣大经。有所未尽。君父一体也。全废及有所未尽。亦有轻重之别。子谦之论。极是极是。然草野之义。不与朝臣同。朝臣则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可也。草野则诚如 仁庙所教言是非则可也。定是非则不可也。弟于二大经。皆各一陈所怀可也。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然止于一者。致仕故也。前陈祢议。不见是而弃拒之。而强聒不舍为不可。故不再疏耳。今疏若又以前既见弃之说。强聒不舍为无妨。则昨年何不再疏乎。昨年丧时。不陈祢疏者。非以上疏为不可也。盖以己试见拒之说。强聒不舍为不可也。今疏并以见拒之说陈辨。则昨年别疏。何为不可乎。昨年别疏与今疏。并陈其为强聒不舍则同矣。其为说不亦支离可厌乎。论语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故今疏但言祢议之可为痛哭。而前疏已尽其辞。故不复论辨耳。下文虽有言及祢议。主意则皆归于讨贼耳。且并陈二意。意未专一。反不如今后更疏之专主祢议也。子
绝和于将来。而徐图养兵。期以五年或七年。大举讨贼。以洗涤前过。此正今日急务也。岂为晚乎。世人不察主意本末。则谤其太晚者固宜矣。不立祢庙。父子大经。全然废灭。和而不讨贼。则君臣大经。有所未尽。君父一体也。全废及有所未尽。亦有轻重之别。子谦之论。极是极是。然草野之义。不与朝臣同。朝臣则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可也。草野则诚如 仁庙所教言是非则可也。定是非则不可也。弟于二大经。皆各一陈所怀可也。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然止于一者。致仕故也。前陈祢议。不见是而弃拒之。而强聒不舍为不可。故不再疏耳。今疏若又以前既见弃之说。强聒不舍为无妨。则昨年何不再疏乎。昨年丧时。不陈祢疏者。非以上疏为不可也。盖以己试见拒之说。强聒不舍为不可也。今疏并以见拒之说陈辨。则昨年别疏。何为不可乎。昨年别疏与今疏。并陈其为强聒不舍则同矣。其为说不亦支离可厌乎。论语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故今疏但言祢议之可为痛哭。而前疏已尽其辞。故不复论辨耳。下文虽有言及祢议。主意则皆归于讨贼耳。且并陈二意。意未专一。反不如今后更疏之专主祢议也。子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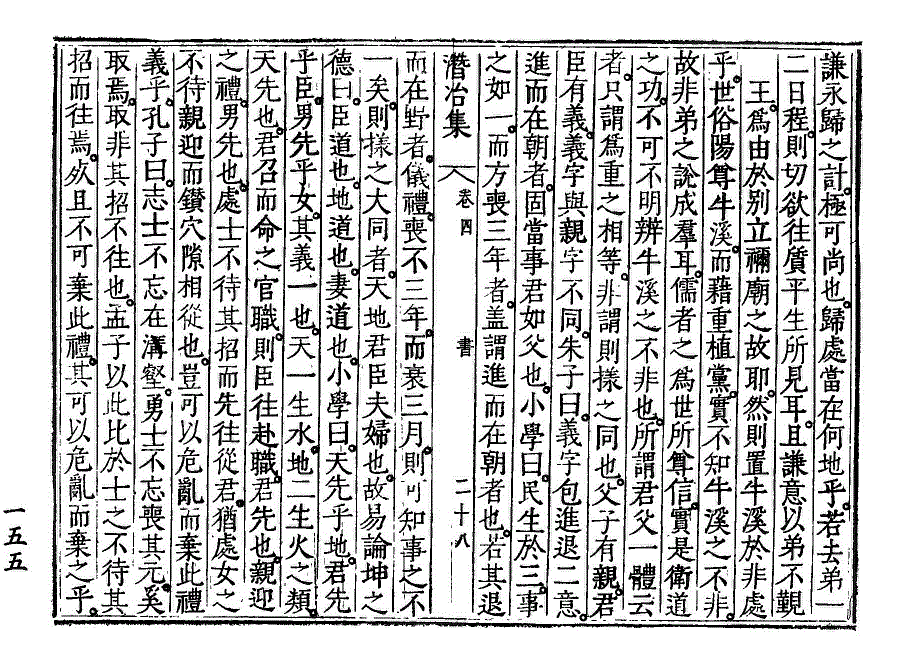 谦永归之计。极可尚也。归处当在何地乎。若去弟一二日程。则切欲往质平生所见耳。且谦意以弟不觐 王。为由于别立祢庙之故耶。然则置牛溪于非处乎。世俗阳尊牛溪。而藉重植党。实不知牛溪之不非。故非弟之说成群耳。儒者之为世所尊信。实是卫道之功。不可不明辨牛溪之不非也。所谓君父一体云者。只谓为重之相等。非谓则样之同也。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义字与亲字不同。朱子曰。义字包进退二意。进而在朝者。固当事君如父也。小学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而方丧三年者。盖谓进而在朝者也。若其退而在野者。仪礼。丧不三年。而衰三月。则可知事之不一矣。则样之大同者。天地君臣夫妇也。故易论坤之德曰。臣道也。地道也。妻道也。小学曰。天先乎地。君先乎臣。男先乎女。其义一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之类。天先也。君召而命之官职。则臣往赴职。君先也。亲迎之礼。男先也。处士不待其招而先往从君。犹处女之不待亲迎而钻穴隙相从也。岂可以危乱而弃此礼义乎。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孟子以此比于士之不待其招而往焉。死且不可弃此礼。其可以危乱而弃之乎。
谦永归之计。极可尚也。归处当在何地乎。若去弟一二日程。则切欲往质平生所见耳。且谦意以弟不觐 王。为由于别立祢庙之故耶。然则置牛溪于非处乎。世俗阳尊牛溪。而藉重植党。实不知牛溪之不非。故非弟之说成群耳。儒者之为世所尊信。实是卫道之功。不可不明辨牛溪之不非也。所谓君父一体云者。只谓为重之相等。非谓则样之同也。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义字与亲字不同。朱子曰。义字包进退二意。进而在朝者。固当事君如父也。小学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而方丧三年者。盖谓进而在朝者也。若其退而在野者。仪礼。丧不三年。而衰三月。则可知事之不一矣。则样之大同者。天地君臣夫妇也。故易论坤之德曰。臣道也。地道也。妻道也。小学曰。天先乎地。君先乎臣。男先乎女。其义一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之类。天先也。君召而命之官职。则臣往赴职。君先也。亲迎之礼。男先也。处士不待其招而先往从君。犹处女之不待亲迎而钻穴隙相从也。岂可以危乱而弃此礼义乎。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孟子以此比于士之不待其招而往焉。死且不可弃此礼。其可以危乱而弃之乎。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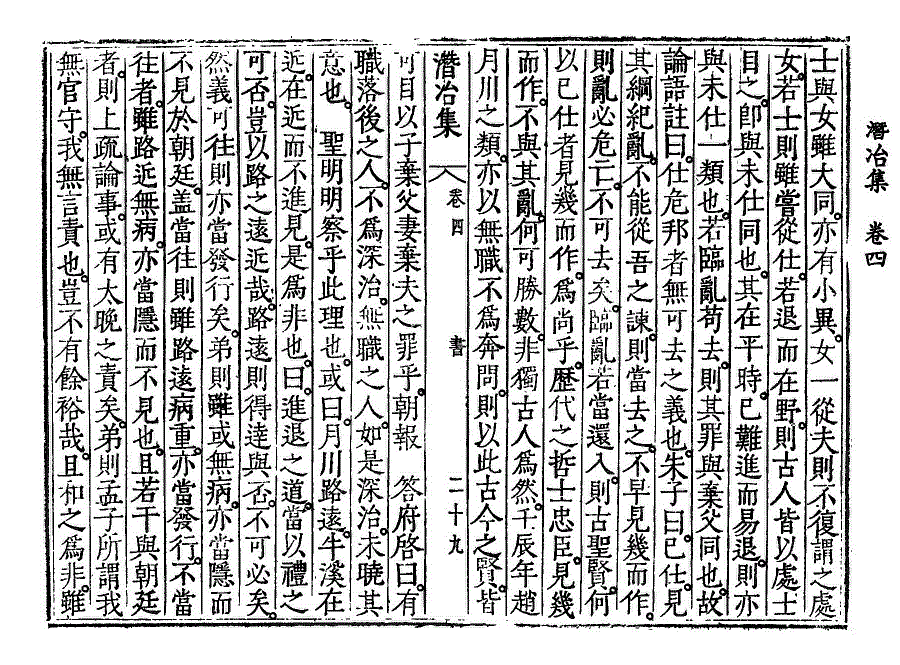 士与女虽大同。亦有小异。女一从夫则不复谓之处女。若士则虽尝从仕。若退而在野。则古人皆以处士目之。即与未仕同也。其在平时。已难进而易退。则亦与未仕一类也。若临乱苟去。则其罪与弃父同也。故论语注曰。仕危邦者无可去之义也。朱子曰。已仕。见其纲纪乱。不能从吾之谏。则当去之。不早见几而作。则乱必危亡。不可去矣。临乱若当还入。则古圣贤。何以已仕者见几而作。为尚乎。历代之哲士忠臣。见几而作。不与其乱。何可胜数。非独古人为然。壬辰年赵月川之类。亦以无职不为奔问。则以此古今之贤。皆可目以子弃父妻弃夫之罪乎。朝报 答府启曰。有职落后之人。不为深治。无职之人。如是深治。未晓其意也。圣 明明察乎此理也。或曰。月川路远。牛溪在近。在近而不进见。是为非也。曰。进退之道。当以礼之可否。岂以路之远近哉。路远则得达与否。不可必矣。然义可往则亦当发行矣。弟则虽或无病。亦当隐而不见于朝廷。盖当往则虽路远病重。亦当发行。不当往者。虽路近无病。亦当隐而不见也。且若干与朝廷者。则上疏论事。或有太晚之责矣。弟则孟子所谓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岂不有馀裕哉。且和之为非。虽
士与女虽大同。亦有小异。女一从夫则不复谓之处女。若士则虽尝从仕。若退而在野。则古人皆以处士目之。即与未仕同也。其在平时。已难进而易退。则亦与未仕一类也。若临乱苟去。则其罪与弃父同也。故论语注曰。仕危邦者无可去之义也。朱子曰。已仕。见其纲纪乱。不能从吾之谏。则当去之。不早见几而作。则乱必危亡。不可去矣。临乱若当还入。则古圣贤。何以已仕者见几而作。为尚乎。历代之哲士忠臣。见几而作。不与其乱。何可胜数。非独古人为然。壬辰年赵月川之类。亦以无职不为奔问。则以此古今之贤。皆可目以子弃父妻弃夫之罪乎。朝报 答府启曰。有职落后之人。不为深治。无职之人。如是深治。未晓其意也。圣 明明察乎此理也。或曰。月川路远。牛溪在近。在近而不进见。是为非也。曰。进退之道。当以礼之可否。岂以路之远近哉。路远则得达与否。不可必矣。然义可往则亦当发行矣。弟则虽或无病。亦当隐而不见于朝廷。盖当往则虽路远病重。亦当发行。不当往者。虽路近无病。亦当隐而不见也。且若干与朝廷者。则上疏论事。或有太晚之责矣。弟则孟子所谓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岂不有馀裕哉。且和之为非。虽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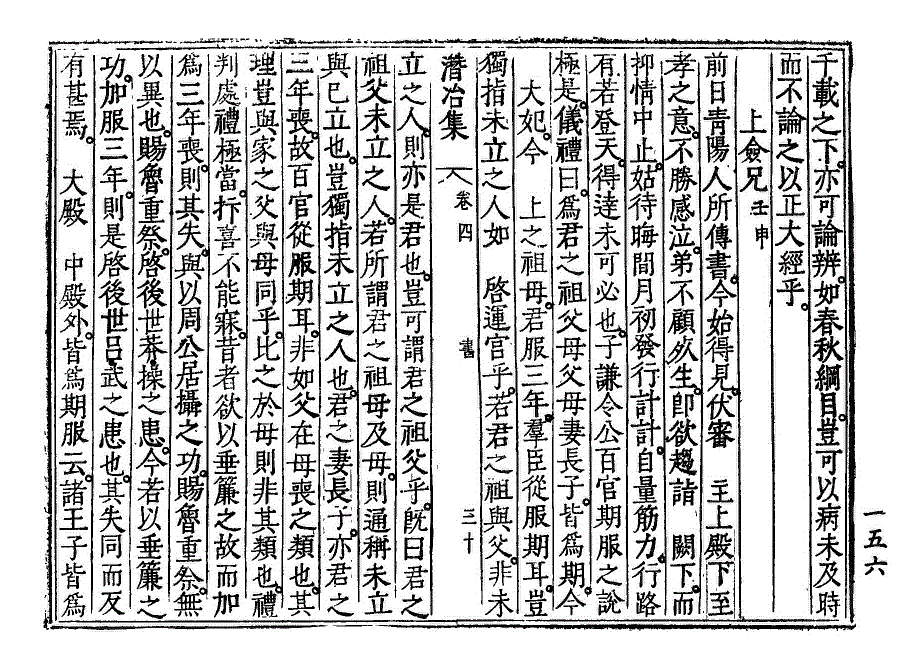 千载之下。亦可论辨。如春秋纲目。岂可以病未及时而不论之以正大经乎。
千载之下。亦可论辨。如春秋纲目。岂可以病未及时而不论之以正大经乎。上佥兄(壬申)
前日青阳人所传书。今始得见。伏审 主上殿下至孝之意。不胜感泣。弟不顾死生。即欲趋诣 阙下。而抑情中止。姑待晦间月初发行计计。自量筋力。行路有若登天。得达未可必也。子谦令公百官期服之说极是。仪礼曰。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长子。皆为期。今 大妃。今 上之祖母。君服三年。群臣从服期耳。岂独指未立之人如 启运宫乎。若君之祖与父。非未立之人。则亦是君也。岂可谓君之祖父乎。既曰君之祖父未立之人。若所谓君之祖母及母。则通称未立与已立也。岂独指未立之人也。君之妻长子。亦君之三年丧。故百官从服期耳。非如父在母丧之类也。其理岂与家之父与母同乎。比之于母则非其类也。礼判处礼极当。抃喜不能寐。昔者欲以垂帘之故而加为三年丧。则其失。与以周公居摄之功。赐鲁重祭。无以异也。赐鲁重祭。启后世莽,操之患。今若以垂帘之功。加服三年。则是启后世吕,武之患也。其失同而反有甚焉。 大殿 中殿外。皆为期服云。诸王子皆为
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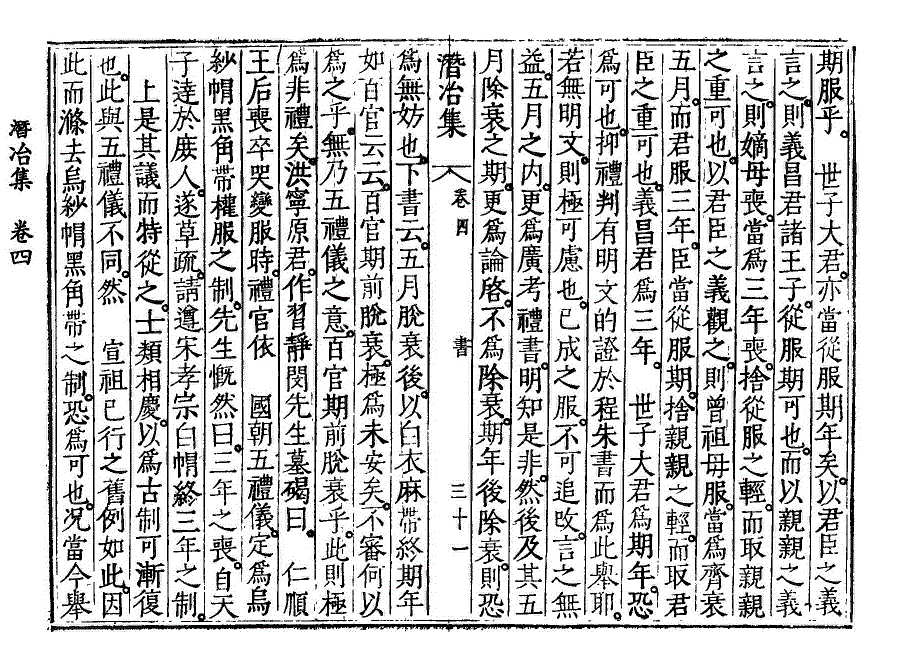 期服乎。 世子大君。亦当从服期年矣。以君臣之义言之。则义昌君诸王子。从服期可也。而以亲亲之义言之。则嫡母丧。当为三年丧。舍从服之轻。而取亲亲之重可也。以君臣之义观之。则曾祖母服。当为齐衰五月。而君服三年。臣当从服期。舍亲亲之轻。而取君臣之重可也。义昌君为三年。 世子大君为期年。恐为可也。抑礼判有明文的證于程朱书而为此举耶。若无明文。则极可虑也。已成之服。不可追改。言之无益。五月之内。更为广考礼书。明知是非。然后及其五月除衰之期。更为论启。不为除衰。期年后除衰。则恐为无妨也。下书云。五月脱衰后。以白衣麻带终期年如百官云云。百官期前脱衰。极为未安矣。不审何以为之乎。无乃五礼仪之意。百官期前脱衰乎。此则极为非礼矣。洪宁原君。作习静闵先生墓碣曰。 仁顺王后丧卒哭变服时。礼官依 国朝五礼仪。定为乌纱帽黑角带权服之制。先生慨然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遂草疏。请遵宋孝宗白帽终三年之制。 上是其议而特从之。士类相庆。以为古制可渐复也。此与五礼仪不同。然 宣祖已行之旧例如此。因此而涤去乌纱帽黑角带之制。恐为可也。况当今举
期服乎。 世子大君。亦当从服期年矣。以君臣之义言之。则义昌君诸王子。从服期可也。而以亲亲之义言之。则嫡母丧。当为三年丧。舍从服之轻。而取亲亲之重可也。以君臣之义观之。则曾祖母服。当为齐衰五月。而君服三年。臣当从服期。舍亲亲之轻。而取君臣之重可也。义昌君为三年。 世子大君为期年。恐为可也。抑礼判有明文的證于程朱书而为此举耶。若无明文。则极可虑也。已成之服。不可追改。言之无益。五月之内。更为广考礼书。明知是非。然后及其五月除衰之期。更为论启。不为除衰。期年后除衰。则恐为无妨也。下书云。五月脱衰后。以白衣麻带终期年如百官云云。百官期前脱衰。极为未安矣。不审何以为之乎。无乃五礼仪之意。百官期前脱衰乎。此则极为非礼矣。洪宁原君。作习静闵先生墓碣曰。 仁顺王后丧卒哭变服时。礼官依 国朝五礼仪。定为乌纱帽黑角带权服之制。先生慨然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遂草疏。请遵宋孝宗白帽终三年之制。 上是其议而特从之。士类相庆。以为古制可渐复也。此与五礼仪不同。然 宣祖已行之旧例如此。因此而涤去乌纱帽黑角带之制。恐为可也。况当今举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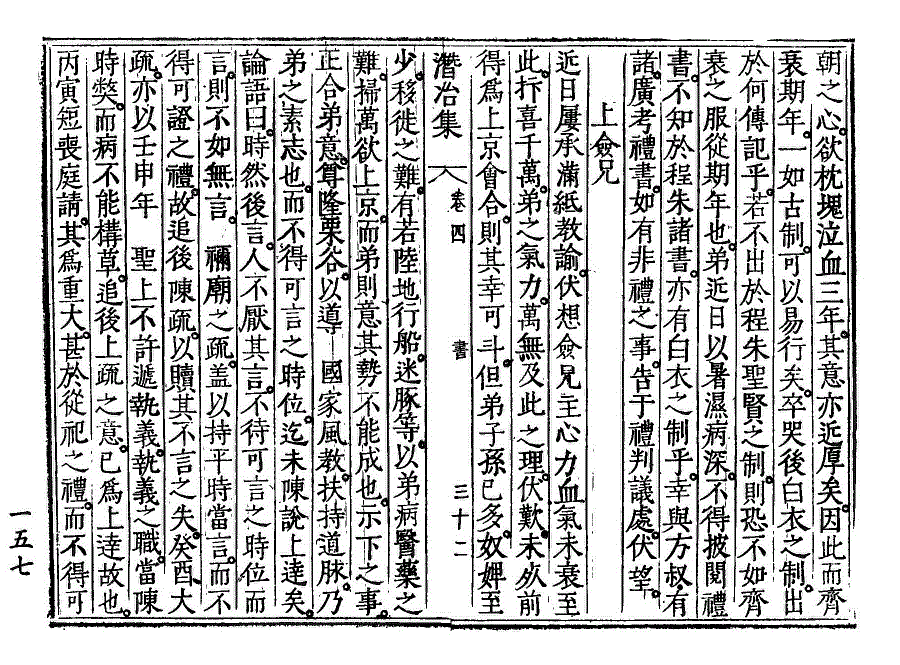 朝之心。欲枕块泣血三年。其意亦近厚矣。因此而齐衰期年。一如古制。可以易行矣。卒哭后白衣之制。出于何传记乎。若不出于程朱圣贤之制。则恐不如齐衰之服从期年也。弟近日以暑湿病深。不得披阅礼书。不知于程朱诸书。亦有白衣之制乎。幸与方叔,有诸。广考礼书。如有非礼之事。告于礼判议处。伏望。
朝之心。欲枕块泣血三年。其意亦近厚矣。因此而齐衰期年。一如古制。可以易行矣。卒哭后白衣之制。出于何传记乎。若不出于程朱圣贤之制。则恐不如齐衰之服从期年也。弟近日以暑湿病深。不得披阅礼书。不知于程朱诸书。亦有白衣之制乎。幸与方叔,有诸。广考礼书。如有非礼之事。告于礼判议处。伏望。上佥兄
近日屡承满纸教谕。伏想佥兄主心力血气未衰至此。抃喜千万。弟之气力。万无及此之理。伏叹。未死前得为上京会合。则其幸可斗。但弟子孙已多。奴婢至少。移徙之难。有若陆地行船。迷豚等。以弟病医药之难。扫万欲上京。而弟则意其势不能成也。示下之事。正合弟意。尊隆栗谷。以导 国家风教。扶持道脉。乃弟之素志也。而不得可言之时位。迄未陈说上达矣。论语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不待可言之时位而言。则不如无言。 祢庙之疏。盖以持平时当言。而不得可證之礼。故追后陈疏。以赎其不言之失。癸酉大疏。亦以壬申年 圣上不许递执义。执义之职。当陈时弊。而病不能构草。追后上疏之意。已为上达故也。丙寅短丧庭请。其为重大。甚于从祀之礼。而不得可
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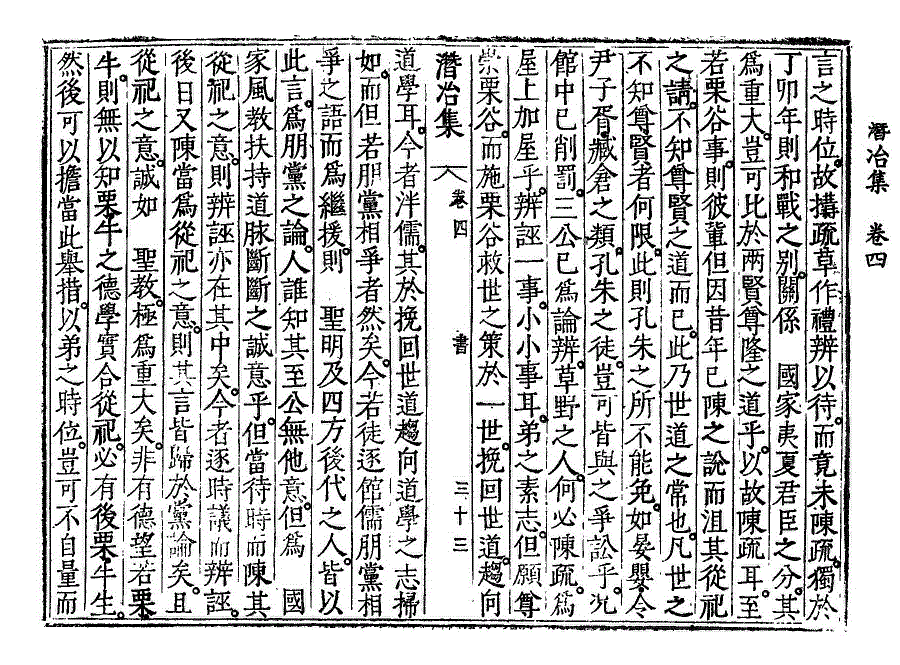 言之时位。故构疏草作礼辨以待。而竟未陈疏。独于丁卯年则和战之别。关系 国家夷夏君臣之分。其为重大。岂可比于两贤尊隆之道乎。以故陈疏耳。至若栗谷事。则彼辈但因昔年已陈之说而沮其从祀之请。不知尊贤之道而已。此乃世道之常也。凡世之不知尊贤者何限。此则孔朱之所不能免。如晏婴,令尹子胥,臧仓之类。孔朱之徒。岂可皆与之争讼乎。况馆中已削罚。三公已为论辨。草野之人。何必陈疏。为屋上加屋乎。辨诬一事。小小事耳。弟之素志。但愿尊崇栗谷。而施栗谷救世之策于一世。挽回世道。趋向道学耳。今者泮儒。其于挽回世道趋向道学之志扫如。而但若朋党相争者然矣。今若徒逐馆儒朋党相争之语而为继援。则 圣明及四方后代之人。皆以此言。为朋党之论。人谁知其至公无他意。但为 国家风教扶持道脉断断之诚意乎。但当待时而陈其从祀之意。则辨诬亦在其中矣。今者逐时议而辨诬。后日又陈当为从祀之意。则其言皆归于党论矣。且从祀之意。诚如 圣教。极为重大矣。非有德望若栗,牛。则无以知栗,牛之德学实合从祀。必有后栗,牛生。然后可以担当此举措。以弟之时位。岂可不自量而
言之时位。故构疏草作礼辨以待。而竟未陈疏。独于丁卯年则和战之别。关系 国家夷夏君臣之分。其为重大。岂可比于两贤尊隆之道乎。以故陈疏耳。至若栗谷事。则彼辈但因昔年已陈之说而沮其从祀之请。不知尊贤之道而已。此乃世道之常也。凡世之不知尊贤者何限。此则孔朱之所不能免。如晏婴,令尹子胥,臧仓之类。孔朱之徒。岂可皆与之争讼乎。况馆中已削罚。三公已为论辨。草野之人。何必陈疏。为屋上加屋乎。辨诬一事。小小事耳。弟之素志。但愿尊崇栗谷。而施栗谷救世之策于一世。挽回世道。趋向道学耳。今者泮儒。其于挽回世道趋向道学之志扫如。而但若朋党相争者然矣。今若徒逐馆儒朋党相争之语而为继援。则 圣明及四方后代之人。皆以此言。为朋党之论。人谁知其至公无他意。但为 国家风教扶持道脉断断之诚意乎。但当待时而陈其从祀之意。则辨诬亦在其中矣。今者逐时议而辨诬。后日又陈当为从祀之意。则其言皆归于党论矣。且从祀之意。诚如 圣教。极为重大矣。非有德望若栗,牛。则无以知栗,牛之德学实合从祀。必有后栗,牛生。然后可以担当此举措。以弟之时位。岂可不自量而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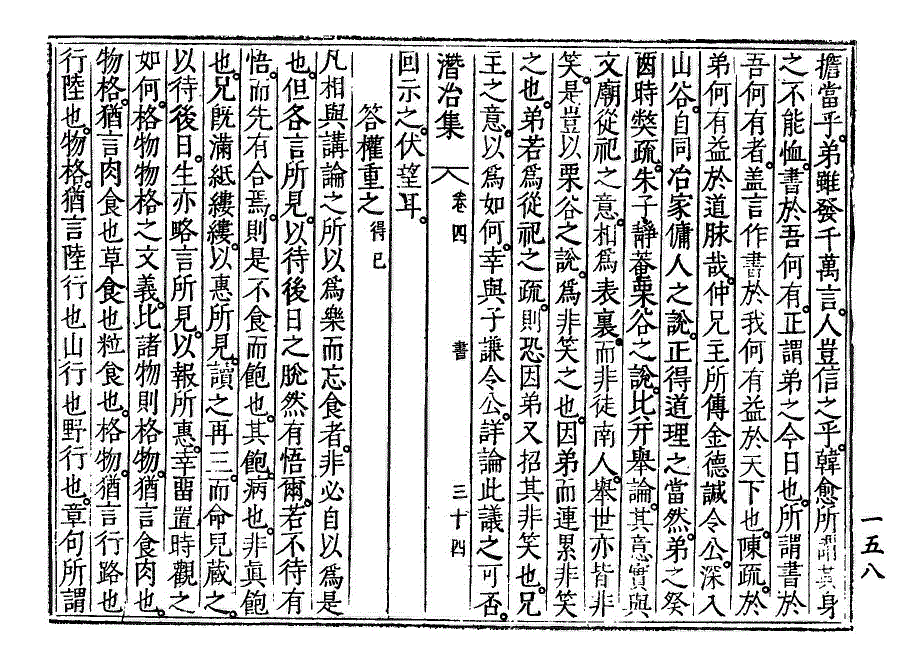 担当乎。弟虽发千万言。人岂信之乎。韩愈所谓其身之不能恤。书于吾何有。正谓弟之今日也。所谓书于吾何有者。盖言作书于我何有益于天下也。陈疏。于弟何有益于道脉哉。仲兄主所传金德諴令公。深入山谷。自同冶家佣人之说。正得道理之当然。弟之癸酉时弊疏。朱子,静庵,栗谷之说。比并举论。其意实与文庙从祀之意。相为表里。而非徒南人。举世亦皆非笑。是岂以栗谷之说。为非笑之也。因弟而连累非笑之也。弟若为从祀之疏。则恐因弟又招其非笑也。兄主之意。以为如何。幸与子谦令公。详论此议之可否。回示之。伏望耳。
担当乎。弟虽发千万言。人岂信之乎。韩愈所谓其身之不能恤。书于吾何有。正谓弟之今日也。所谓书于吾何有者。盖言作书于我何有益于天下也。陈疏。于弟何有益于道脉哉。仲兄主所传金德諴令公。深入山谷。自同冶家佣人之说。正得道理之当然。弟之癸酉时弊疏。朱子,静庵,栗谷之说。比并举论。其意实与文庙从祀之意。相为表里。而非徒南人。举世亦皆非笑。是岂以栗谷之说。为非笑之也。因弟而连累非笑之也。弟若为从祀之疏。则恐因弟又招其非笑也。兄主之意。以为如何。幸与子谦令公。详论此议之可否。回示之。伏望耳。答权重之(得己)
凡相与讲论之所以为乐而忘食者。非必自以为是也。但各言所见。以待后日之脱然有悟尔。若不待有悟。而先有合焉。则是不食而饱也。其饱。病也。非真饱也。兄既满纸缕缕。以惠所见。读之再三。而命儿藏之。以待后日。生亦略言所见。以报所惠。幸留置时观之如何。格物物格之文义。比诸物则格物。犹言食肉也。物格。犹言肉食也草食也粒食也。格物。犹言行路也行陆也。物格。犹言陆行也山行也野行也。章句所谓
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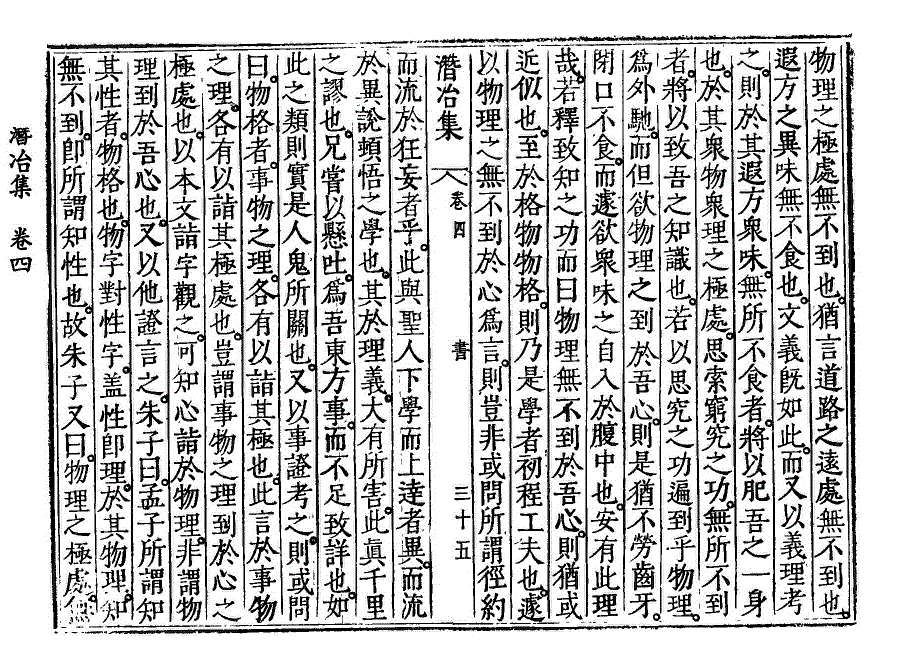 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犹言道路之远处无不到也。遐方之异味无不食也。文义既如此。而又以义理考之。则于其遐方众味。无所不食者。将以肥吾之一身也。于其众物众理之极处。思索穷究之功。无所不到者。将以致吾之知识也。若以思究之功遍到乎物理。为外驰。而但欲物理之到于吾心。则是犹不劳齿牙。闭口不食。而遽欲众味之自入于腹中也。安有此理哉。若释致知之功而曰物理无不到于吾心。则犹或近似也。至于格物物格。则乃是学者初程工夫也。遽以物理之无不到于心为言。则岂非或问所谓径约而流于狂妄者乎。此与圣人下学而上达者异。而流于异说顿悟之学也。其于理义。大有所害。此真千里之谬也。兄尝以悬吐。为吾东方事。而不足致详也。如此之类则实是人鬼所关也。又以事證考之。则或问曰。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诣其极也。此言于事物之理。各有以诣其极处也。岂谓事物之理到于心之极处也。以本文诣字观之。可知心诣于物理。非谓物理到于吾心也。又以他證言之。朱子曰。孟子所谓知其性者。物格也。物字对性字。盖性即理。于其物理。知无不到。即所谓知性也。故朱子又曰。物理之极处。无
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犹言道路之远处无不到也。遐方之异味无不食也。文义既如此。而又以义理考之。则于其遐方众味。无所不食者。将以肥吾之一身也。于其众物众理之极处。思索穷究之功。无所不到者。将以致吾之知识也。若以思究之功遍到乎物理。为外驰。而但欲物理之到于吾心。则是犹不劳齿牙。闭口不食。而遽欲众味之自入于腹中也。安有此理哉。若释致知之功而曰物理无不到于吾心。则犹或近似也。至于格物物格。则乃是学者初程工夫也。遽以物理之无不到于心为言。则岂非或问所谓径约而流于狂妄者乎。此与圣人下学而上达者异。而流于异说顿悟之学也。其于理义。大有所害。此真千里之谬也。兄尝以悬吐。为吾东方事。而不足致详也。如此之类则实是人鬼所关也。又以事證考之。则或问曰。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诣其极也。此言于事物之理。各有以诣其极处也。岂谓事物之理到于心之极处也。以本文诣字观之。可知心诣于物理。非谓物理到于吾心也。又以他證言之。朱子曰。孟子所谓知其性者。物格也。物字对性字。盖性即理。于其物理。知无不到。即所谓知性也。故朱子又曰。物理之极处。无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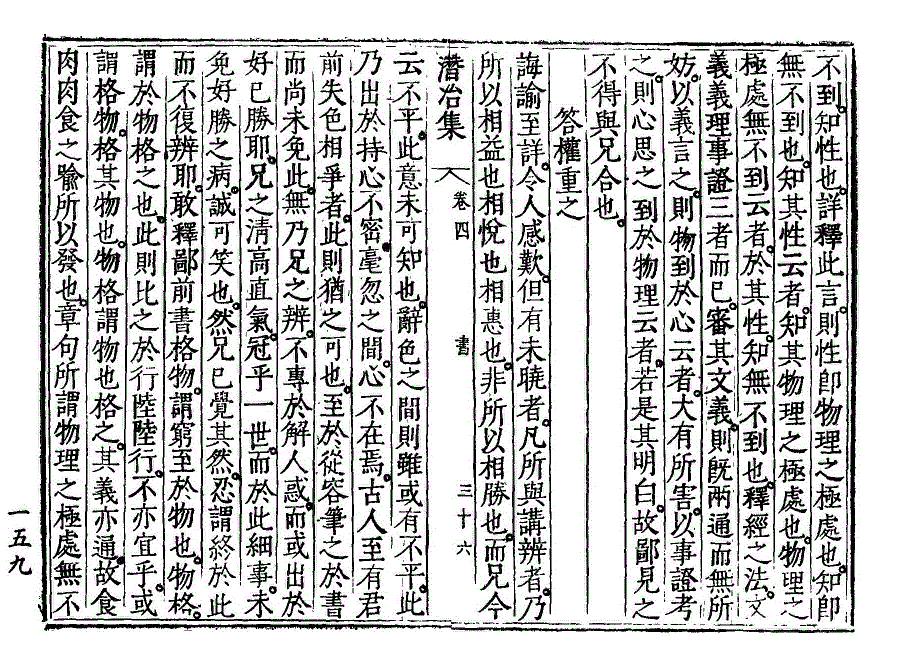 不到。知性也。详释此言。则性即物理之极处也。知即无不到也。知其性云者。知其物理之极处也。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云者。于其性。知无不到也。释经之法。文义义理事證三者而已。审其文义。则既两通而无所妨。以义言之。则物到于心云者。大有所害。以事證考之。则心思之到于物理云者。若是其明白。故鄙见之不得与兄合也。
不到。知性也。详释此言。则性即物理之极处也。知即无不到也。知其性云者。知其物理之极处也。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云者。于其性。知无不到也。释经之法。文义义理事證三者而已。审其文义。则既两通而无所妨。以义言之。则物到于心云者。大有所害。以事證考之。则心思之到于物理云者。若是其明白。故鄙见之不得与兄合也。答权重之
诲谕至详。令人感叹。但有未晓者。凡所与讲辨者。乃所以相益也相悦也相惠也。非所以相胜也。而兄今云不平。此意未可知也。辞色之间则虽或有不平。此乃出于持心不密。毫忽之间。心不在焉。古人至有君前失色相争者。此则犹之可也。至于从容笔之于书而尚未免此。无乃兄之辨。不专于解人惑。而或出于好已胜耶。兄之清高直气。冠乎一世。而于此细事。未免好胜之病。诚可笑也。然兄已觉其然。忍谓终于此而不复辨耶。敢释鄙前书格物。谓穷至于物也。物格。谓于物格之也。此则比之于行陆陆行。不亦宜乎。或谓格物。格其物也。物格谓物也格之。其义亦通。故食肉肉食之喻所以发也。章句所谓物理之极处无不
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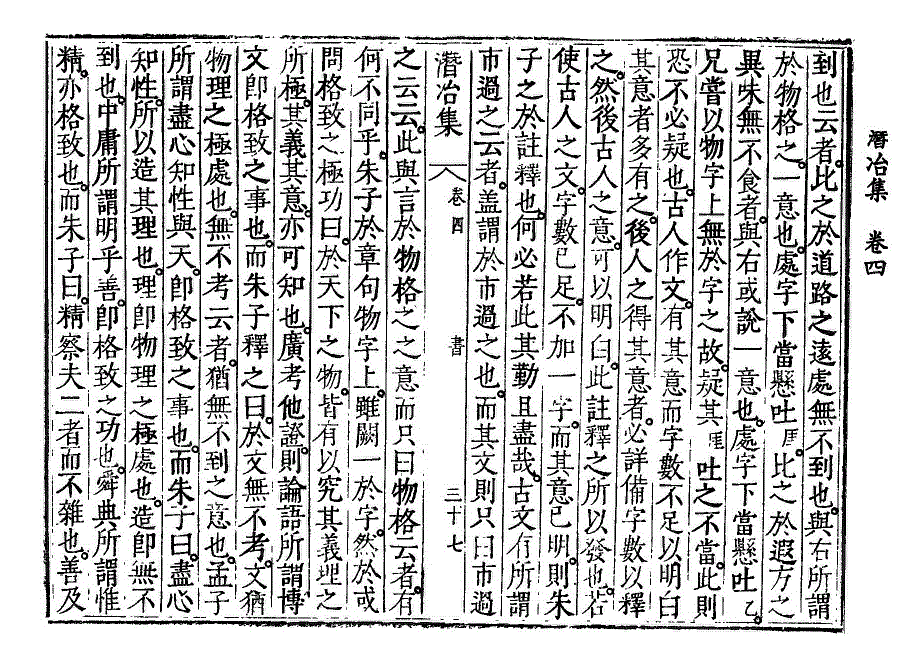 到也云者。比之于道路之远处无不到也。与右所谓于物格之。一意也。处字下当悬吐(厓)。比之于遐方之异味无不食者。与右或说一意也。处字下当悬吐(乙)。兄尝以物字上无于字之故。疑其(厓)吐之不当。此则恐不必疑也。古人作文。有其意而字数不足以明白其意者多有之。后人之得其意者。必详备字数以释之。然后古人之意。可以明白。此注释之所以发也。若使古人之文。字数已足。不加一字。而其意已明。则朱子之于注释也。何必若此其勤且尽哉。古文有所谓市过之云者。盖谓于市过之也。而其文则只曰市过之云云。此与言于物格之之意而只曰物格云者。有何不同乎。朱子于章句物字上。虽阙一于字。然于或问格致之极功曰。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义埋之所极。其义其意。亦可知也。广考他證。则论语所谓博文即格致之事也。而朱子释之曰。于文无不考。文犹物理之极处也。无不考云者。犹无不到之意也。孟子所谓尽心知性与天。即格致之事也。而朱子曰。尽心知性。所以造其理也。理即物理之极处也。造即无不到也。中庸所谓明乎善。即格致之功也。舜典所谓惟精。亦格致也。而朱子曰。精察夫二者而不杂也。善及
到也云者。比之于道路之远处无不到也。与右所谓于物格之。一意也。处字下当悬吐(厓)。比之于遐方之异味无不食者。与右或说一意也。处字下当悬吐(乙)。兄尝以物字上无于字之故。疑其(厓)吐之不当。此则恐不必疑也。古人作文。有其意而字数不足以明白其意者多有之。后人之得其意者。必详备字数以释之。然后古人之意。可以明白。此注释之所以发也。若使古人之文。字数已足。不加一字。而其意已明。则朱子之于注释也。何必若此其勤且尽哉。古文有所谓市过之云者。盖谓于市过之也。而其文则只曰市过之云云。此与言于物格之之意而只曰物格云者。有何不同乎。朱子于章句物字上。虽阙一于字。然于或问格致之极功曰。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义埋之所极。其义其意。亦可知也。广考他證。则论语所谓博文即格致之事也。而朱子释之曰。于文无不考。文犹物理之极处也。无不考云者。犹无不到之意也。孟子所谓尽心知性与天。即格致之事也。而朱子曰。尽心知性。所以造其理也。理即物理之极处也。造即无不到也。中庸所谓明乎善。即格致之功也。舜典所谓惟精。亦格致也。而朱子曰。精察夫二者而不杂也。善及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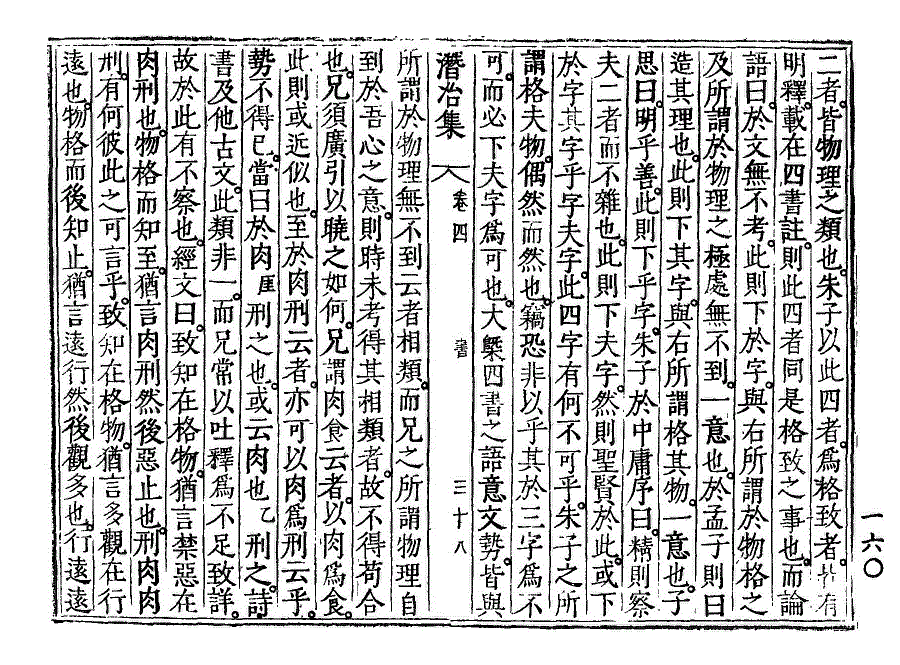 二者。皆物理之类也。朱子以此四者。为格致者。皆有明释。载在四书注。则此四者同是格致之事也。而论语曰。于文无不考。此则下于字。与右所谓于物格之及所谓于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一意也。于孟子则曰造其理也。此则下其字。与右所谓格其物。一意也。子思曰。明乎善。此则下乎字。朱子于中庸序曰。精则察夫二者而不杂也。此则下夫字。然则圣贤于此。或下于字其字乎字夫字。此四字有何不可乎。朱子之所谓格夫物。偶然而然也。窃恐非以乎其于三字为不可。而必下夫字为可也。大槩四书之语意文势。皆与所谓于物理无不到云者相类。而兄之所谓物理自到于吾心之意。则时未考得其相类者。故不得苟合也。兄须广引以晓之如何。兄谓肉食云者。以肉为食。此则或近似也。至于肉刑云者。亦可以肉为刑云乎。势不得已。当曰于肉(厓)刑之也。或云肉也(乙)刑之。诗,书及他古文。此类非一。而兄常以吐释为不足致详。故于此有不察也。经文曰。致知在格物。犹言禁恶在肉刑也。物格而知至。犹言肉刑然后恶止也。刑肉肉刑。有何彼此之可言乎。致知在格物。犹言多观在行远也。物格而后知止。犹言远行然后观多也。行远远
二者。皆物理之类也。朱子以此四者。为格致者。皆有明释。载在四书注。则此四者同是格致之事也。而论语曰。于文无不考。此则下于字。与右所谓于物格之及所谓于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一意也。于孟子则曰造其理也。此则下其字。与右所谓格其物。一意也。子思曰。明乎善。此则下乎字。朱子于中庸序曰。精则察夫二者而不杂也。此则下夫字。然则圣贤于此。或下于字其字乎字夫字。此四字有何不可乎。朱子之所谓格夫物。偶然而然也。窃恐非以乎其于三字为不可。而必下夫字为可也。大槩四书之语意文势。皆与所谓于物理无不到云者相类。而兄之所谓物理自到于吾心之意。则时未考得其相类者。故不得苟合也。兄须广引以晓之如何。兄谓肉食云者。以肉为食。此则或近似也。至于肉刑云者。亦可以肉为刑云乎。势不得已。当曰于肉(厓)刑之也。或云肉也(乙)刑之。诗,书及他古文。此类非一。而兄常以吐释为不足致详。故于此有不察也。经文曰。致知在格物。犹言禁恶在肉刑也。物格而知至。犹言肉刑然后恶止也。刑肉肉刑。有何彼此之可言乎。致知在格物。犹言多观在行远也。物格而后知止。犹言远行然后观多也。行远远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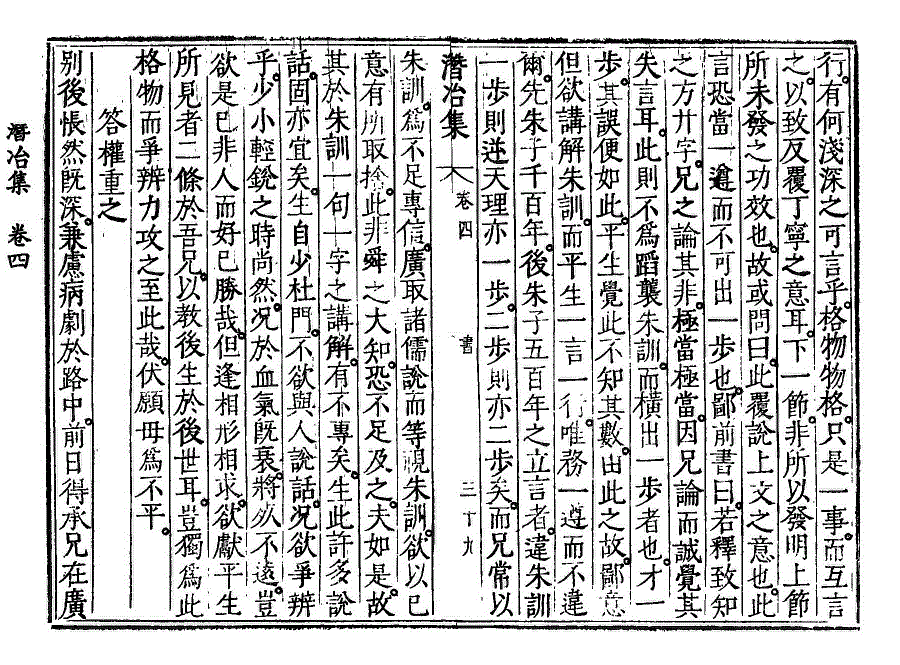 行。有何浅深之可言乎。格物物格。只是一事。而互言之。以致反覆丁宁之意耳。下一节。非所以发明上节所未发之功效也。故或问曰。此覆说上文之意也。此言恐当一遵而不可出一步也。鄙前书曰。若释致知之方廿字。兄之论其非。极当极当。因兄论而诚觉其失言耳。此则不为蹈袭朱训。而横出一步者也。才一步。其误便如此。平生觉此不知其数。由此之故。鄙意但欲讲解朱训。而平生一言一行。唯务一遵而不违尔。先朱子千百年。后朱子五百年之立言者。违朱训一步则逆天理亦一步。二步则亦二步矣。而兄常以朱训。为不足专信。广取诸儒说而等视朱训。欲以已意有所取舍。此非舜之大知。恐不足及之。夫如是。故其于朱训一句一字之讲解。有不专矣。生此许多说话。固亦宜矣。生自少杜门。不欲与人说话。况欲争辨乎。少小轻锐之时尚然。况于血气既衰。将死不远。岂欲是己非人而好已胜哉。但逢相形相求。欲献平生所见者二条于吾兄。以教后生于后世耳。岂独为此格物而争辨力攻之至此哉。伏愿毋为不平。
行。有何浅深之可言乎。格物物格。只是一事。而互言之。以致反覆丁宁之意耳。下一节。非所以发明上节所未发之功效也。故或问曰。此覆说上文之意也。此言恐当一遵而不可出一步也。鄙前书曰。若释致知之方廿字。兄之论其非。极当极当。因兄论而诚觉其失言耳。此则不为蹈袭朱训。而横出一步者也。才一步。其误便如此。平生觉此不知其数。由此之故。鄙意但欲讲解朱训。而平生一言一行。唯务一遵而不违尔。先朱子千百年。后朱子五百年之立言者。违朱训一步则逆天理亦一步。二步则亦二步矣。而兄常以朱训。为不足专信。广取诸儒说而等视朱训。欲以已意有所取舍。此非舜之大知。恐不足及之。夫如是。故其于朱训一句一字之讲解。有不专矣。生此许多说话。固亦宜矣。生自少杜门。不欲与人说话。况欲争辨乎。少小轻锐之时尚然。况于血气既衰。将死不远。岂欲是己非人而好已胜哉。但逢相形相求。欲献平生所见者二条于吾兄。以教后生于后世耳。岂独为此格物而争辨力攻之至此哉。伏愿毋为不平。答权重之
别后怅然既深。兼虑病剧于路中。前日得承兄在广
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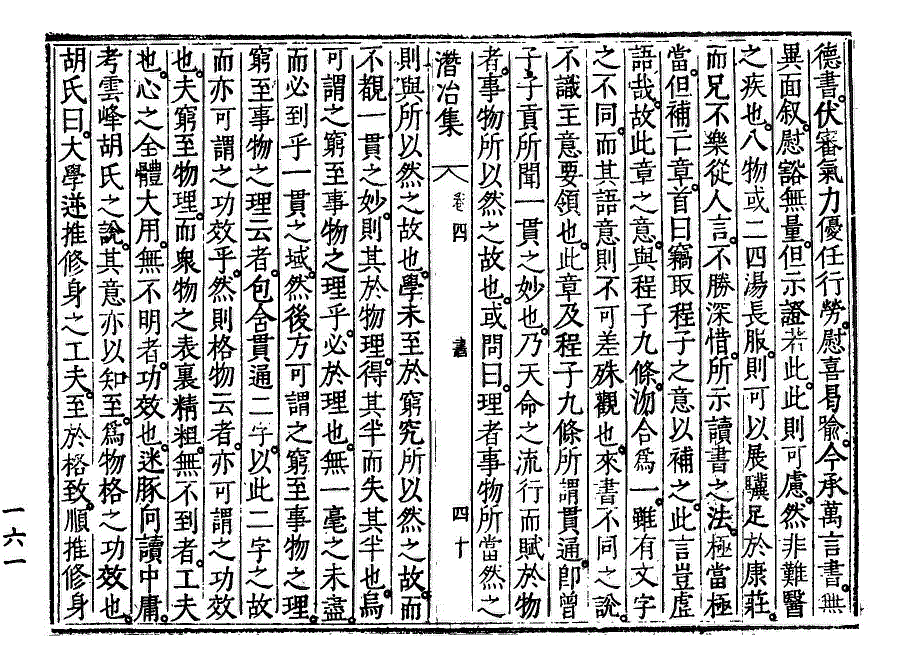 德书。伏审气力优任行劳。慰喜曷喻。今承万言书。无异面叙。慰豁无量。但示證若此。此则可虑。然非难医之疾也。八物或二四汤长服。则可以展骥足于康庄。而兄不乐从人言。不胜深惜。所示读书之法。极当极当。但补亡章。首曰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此言岂虚语哉。故此章之意。与程子九条。沕合为一。虽有文字之不同。而其语意则不可差殊观也。来书不同之说。不识主意要领也。此章及程子九条所谓贯通。即曾子,子贡所闻一贯之妙也。乃天命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事物所以然之故也。或问曰。理者事物所当然之则与所以然之故也。学未至于穷究所以然之故。而不睹一贯之妙。则其于物理。得其半而失其半也。乌可谓之穷至事物之理乎。必于理也。无一毫之未尽。而必到乎一贯之域。然后方可谓之穷至事物之理。穷至事物之理云者。包含贯通二字。以此二字之故而亦可谓之功效乎。然则格物云者。亦可谓之功效也。夫穷至物理。而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者。工夫也。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者。功效也。迷豚向读中庸。考云峰胡氏之说。其意亦以知至。为物格之功效也。胡氏曰。大学逆推修身之工夫。至于格致。顺推修身
德书。伏审气力优任行劳。慰喜曷喻。今承万言书。无异面叙。慰豁无量。但示證若此。此则可虑。然非难医之疾也。八物或二四汤长服。则可以展骥足于康庄。而兄不乐从人言。不胜深惜。所示读书之法。极当极当。但补亡章。首曰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此言岂虚语哉。故此章之意。与程子九条。沕合为一。虽有文字之不同。而其语意则不可差殊观也。来书不同之说。不识主意要领也。此章及程子九条所谓贯通。即曾子,子贡所闻一贯之妙也。乃天命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事物所以然之故也。或问曰。理者事物所当然之则与所以然之故也。学未至于穷究所以然之故。而不睹一贯之妙。则其于物理。得其半而失其半也。乌可谓之穷至事物之理乎。必于理也。无一毫之未尽。而必到乎一贯之域。然后方可谓之穷至事物之理。穷至事物之理云者。包含贯通二字。以此二字之故而亦可谓之功效乎。然则格物云者。亦可谓之功效也。夫穷至物理。而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者。工夫也。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者。功效也。迷豚向读中庸。考云峰胡氏之说。其意亦以知至。为物格之功效也。胡氏曰。大学逆推修身之工夫。至于格致。顺推修身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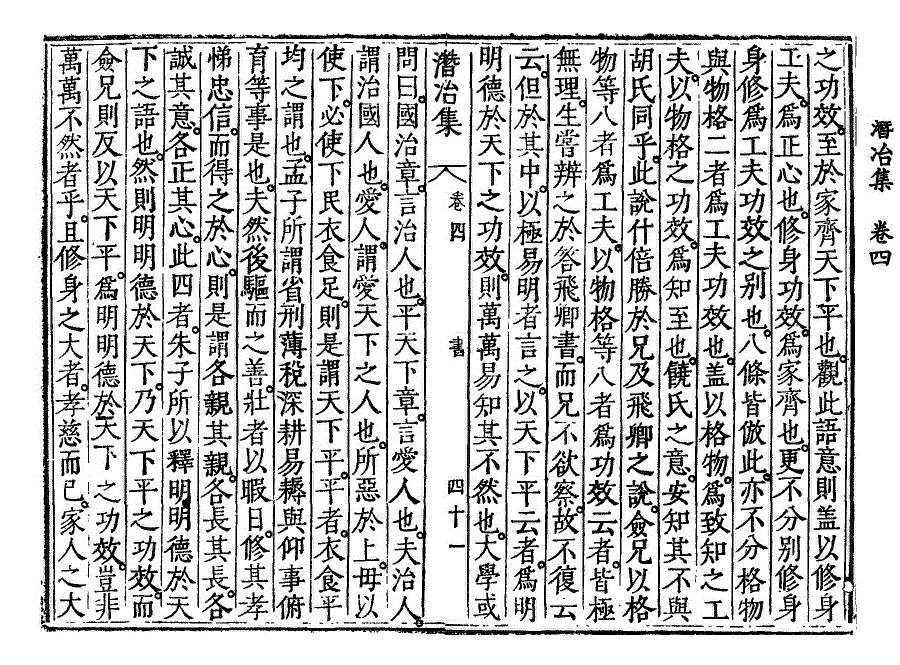 之功效。至于家齐天下平也。观此语意则盖以修身工夫。为正心也。修身功效。为家齐也。更不分别修身身修为工夫功效之别也。八条皆仿此。亦不分格物与物格二者为工夫功效也。盖以格物。为致知之工夫。以物格之功效。为知至也。饶氏之意。安知其不与胡氏同乎。此说什倍胜于兄及飞卿之说。佥兄以格物等八者为工夫。以物格等八者为功效云者。皆极无理。生尝辨之于答飞卿书。而兄不欲察。故不复云云。但于其中。以极易明者言之。以天下平云者。为明明德于天下之功效。则万万易知其不然也。大学或问曰。国治章。言治人也。平天下章。言爱人也。夫治人。谓治国人也。爱人。谓爱天下之人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必使下民衣食足。则是谓天下平。平者。衣食平均之谓也。孟子所谓省刑薄税深耕易耨与仰事俯育等事是也。夫然后驱而之善。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而得之于心。则是谓各亲其亲。各长其长。各诚其意。各正其心。此四者。朱子所以释明。明德于天下之语也。然则明明德于天下。乃天下平之功效。而佥兄则反以天下平。为明明德于天下之功效。岂非万万不然者乎。且修身之大者。孝慈而已。家人之大
之功效。至于家齐天下平也。观此语意则盖以修身工夫。为正心也。修身功效。为家齐也。更不分别修身身修为工夫功效之别也。八条皆仿此。亦不分格物与物格二者为工夫功效也。盖以格物。为致知之工夫。以物格之功效。为知至也。饶氏之意。安知其不与胡氏同乎。此说什倍胜于兄及飞卿之说。佥兄以格物等八者为工夫。以物格等八者为功效云者。皆极无理。生尝辨之于答飞卿书。而兄不欲察。故不复云云。但于其中。以极易明者言之。以天下平云者。为明明德于天下之功效。则万万易知其不然也。大学或问曰。国治章。言治人也。平天下章。言爱人也。夫治人。谓治国人也。爱人。谓爱天下之人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必使下民衣食足。则是谓天下平。平者。衣食平均之谓也。孟子所谓省刑薄税深耕易耨与仰事俯育等事是也。夫然后驱而之善。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而得之于心。则是谓各亲其亲。各长其长。各诚其意。各正其心。此四者。朱子所以释明。明德于天下之语也。然则明明德于天下。乃天下平之功效。而佥兄则反以天下平。为明明德于天下之功效。岂非万万不然者乎。且修身之大者。孝慈而已。家人之大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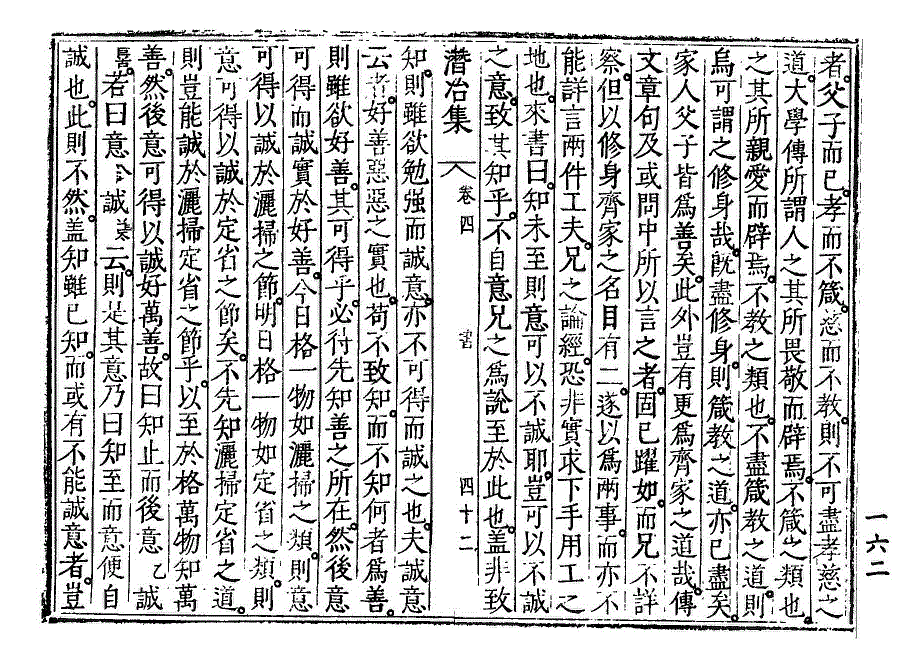 者。父子而已。孝而不箴。慈而不教。则不可尽孝慈之道。大学传所谓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不箴之类也。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不教之类也。不尽箴教之道。则乌可谓之修身哉。既尽修身。则箴教之道。亦已尽矣。家人父子皆为善矣。此外岂有更为齐家之道哉。传文章句及或问中所以言之者。固已跃如。而兄不详察。但以修身齐家之名目有二。遂以为两事。而亦不能详言两件工夫。兄之论经。恐非实求下手用工之地也。来书曰。知未至则意可以不诚耶。岂可以不诚之意。致其知乎。不自意兄之为说至于此也。盖非致知。则虽欲勉强而诚意。亦不可得而诚之也。夫诚意云者。好善恶恶之实也。苟不致知。而不知何者为善。则虽欲好善。其可得乎。必待先知善之所在。然后意可得而诚实于好善。今日格一物如洒扫之类。则意可得以诚于洒扫之节。明日格一物如定省之类。则意可得以诚于定省之节矣。不先知洒扫定省之道。则岂能诚于洒扫定省之节乎。以至于格万物知万善。然后意可得以诚好万善。故曰知止而后意(乙)诚(巨古)。若曰意▒诚(▒)云。则是其意乃曰知至而意便自诚也。此则不然。盖知虽已知。而或有不能诚意者。岂
者。父子而已。孝而不箴。慈而不教。则不可尽孝慈之道。大学传所谓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不箴之类也。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不教之类也。不尽箴教之道。则乌可谓之修身哉。既尽修身。则箴教之道。亦已尽矣。家人父子皆为善矣。此外岂有更为齐家之道哉。传文章句及或问中所以言之者。固已跃如。而兄不详察。但以修身齐家之名目有二。遂以为两事。而亦不能详言两件工夫。兄之论经。恐非实求下手用工之地也。来书曰。知未至则意可以不诚耶。岂可以不诚之意。致其知乎。不自意兄之为说至于此也。盖非致知。则虽欲勉强而诚意。亦不可得而诚之也。夫诚意云者。好善恶恶之实也。苟不致知。而不知何者为善。则虽欲好善。其可得乎。必待先知善之所在。然后意可得而诚实于好善。今日格一物如洒扫之类。则意可得以诚于洒扫之节。明日格一物如定省之类。则意可得以诚于定省之节矣。不先知洒扫定省之道。则岂能诚于洒扫定省之节乎。以至于格万物知万善。然后意可得以诚好万善。故曰知止而后意(乙)诚(巨古)。若曰意▒诚(▒)云。则是其意乃曰知至而意便自诚也。此则不然。盖知虽已知。而或有不能诚意者。岂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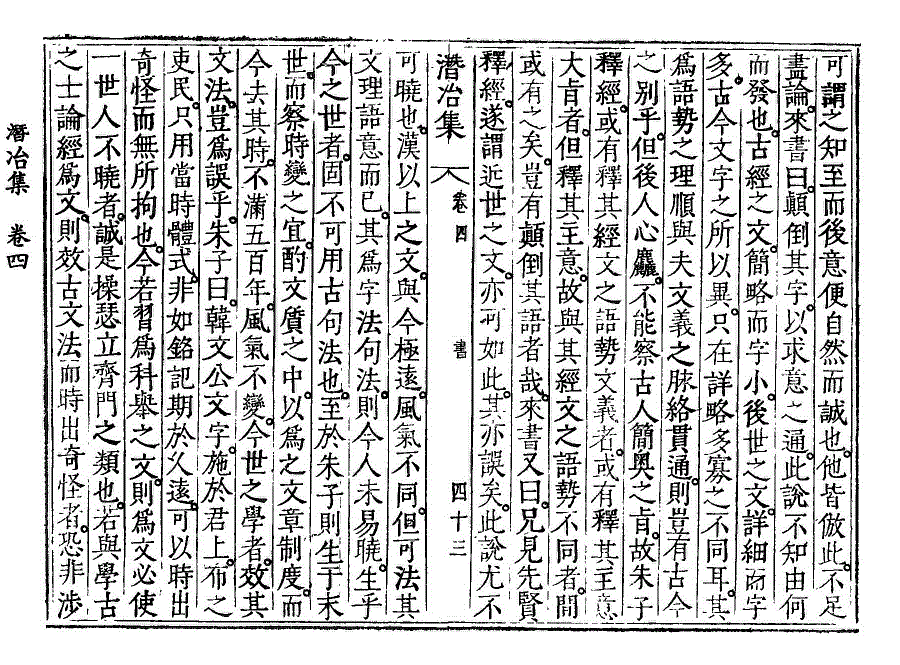 可谓之知至而后意便自然而诚也。他皆仿此。不足尽论。来书曰。颠倒其字。以求意之通。此说不知由何而发也。古经之文。简略而字小。后世之文。详细而字多。古今文字之所以异。只在详略多寡之不同耳。其为语势之理顺与夫文义之脉络贯通。则岂有古今之别乎。但后人心粗。不能察古人简奥之旨。故朱子释经。或有释其经文之语势文义者。或有释其王意大旨者。但释其主意。故与其经文之语势不同者。间或有之矣。岂有颠倒其语者哉。来书又曰。兄见先贤释经。遂谓近世之文。亦可如此。其亦误矣。此说尤不可晓也汉以上之文与今极远。风气不同但可法其文理语意而已。其为字法句法。则今人未易晓。生乎今之世者。固不可用古句法也。至于朱子则生于末世。而察时变之宜。酌文质之中。以为之文章制度。而今去其时。不满五百年。风气不变。今世之学者。效其文法。岂为误乎。朱子曰。韩文公文字。施于君上。布之吏民。只用当时体式。非如铭记期于久远。可以时出奇怪而无所拘也。今若习为科举之文。则为文必使一世人不晓者。诚是操瑟立齐门之类也。若与学古之士论经为文。则效古文法而时出奇怪者。恐非涉
可谓之知至而后意便自然而诚也。他皆仿此。不足尽论。来书曰。颠倒其字。以求意之通。此说不知由何而发也。古经之文。简略而字小。后世之文。详细而字多。古今文字之所以异。只在详略多寡之不同耳。其为语势之理顺与夫文义之脉络贯通。则岂有古今之别乎。但后人心粗。不能察古人简奥之旨。故朱子释经。或有释其经文之语势文义者。或有释其王意大旨者。但释其主意。故与其经文之语势不同者。间或有之矣。岂有颠倒其语者哉。来书又曰。兄见先贤释经。遂谓近世之文。亦可如此。其亦误矣。此说尤不可晓也汉以上之文与今极远。风气不同但可法其文理语意而已。其为字法句法。则今人未易晓。生乎今之世者。固不可用古句法也。至于朱子则生于末世。而察时变之宜。酌文质之中。以为之文章制度。而今去其时。不满五百年。风气不变。今世之学者。效其文法。岂为误乎。朱子曰。韩文公文字。施于君上。布之吏民。只用当时体式。非如铭记期于久远。可以时出奇怪而无所拘也。今若习为科举之文。则为文必使一世人不晓者。诚是操瑟立齐门之类也。若与学古之士论经为文。则效古文法而时出奇怪者。恐非涉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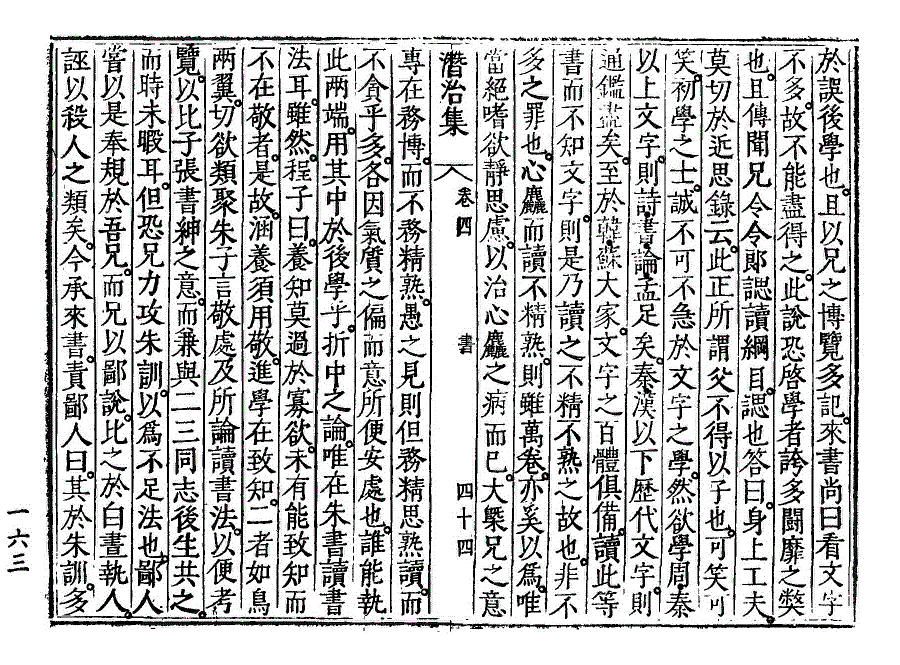 于误后学也。且以兄之博览多记。来书尚曰看文字不多。故不能尽得之。此说恐启学者誇多斗靡之弊也。且传闻兄令令郎諰读纲目。諰也答曰。身上工夫。莫切于近思录云。此正所谓父不得以子也。可笑可笑。初学之士。诚不可不急于文字之学。然欲学周,秦以上文字。则诗,书,论,孟足矣。秦,汉以下历代文字。则通鉴尽矣。至于韩,苏大家。文字之百体俱备。读此等书而不知文字。则是乃读之不精不熟之故也。非不多之罪也。心粗而读不精熟。则虽万卷。亦奚以为。唯当绝嗜欲静思虑。以治心粗之病而已。大槩兄之意专在务博。而不务精熟。愚之见则但务精思熟读。而不贪乎多。各因气质之偏而意所便安处也。谁能执此两端。用其中于后学乎。折中之论。唯在朱书读书法耳。虽然。程子曰。养知莫过于寡欲。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是故。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二者如鸟两翼。切欲类聚朱子言敬处及所论读书法。以便考览。以比子张书绅之意。而兼与二三同志后生共之。而时未暇耳。但恐兄力攻朱训。以为不足法也。鄙人尝以是奉规于吾兄。而兄以鄙说。比之于白昼执人。诬以杀人之类矣。今承来书。责鄙人曰。其于朱训。多
于误后学也。且以兄之博览多记。来书尚曰看文字不多。故不能尽得之。此说恐启学者誇多斗靡之弊也。且传闻兄令令郎諰读纲目。諰也答曰。身上工夫。莫切于近思录云。此正所谓父不得以子也。可笑可笑。初学之士。诚不可不急于文字之学。然欲学周,秦以上文字。则诗,书,论,孟足矣。秦,汉以下历代文字。则通鉴尽矣。至于韩,苏大家。文字之百体俱备。读此等书而不知文字。则是乃读之不精不熟之故也。非不多之罪也。心粗而读不精熟。则虽万卷。亦奚以为。唯当绝嗜欲静思虑。以治心粗之病而已。大槩兄之意专在务博。而不务精熟。愚之见则但务精思熟读。而不贪乎多。各因气质之偏而意所便安处也。谁能执此两端。用其中于后学乎。折中之论。唯在朱书读书法耳。虽然。程子曰。养知莫过于寡欲。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是故。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二者如鸟两翼。切欲类聚朱子言敬处及所论读书法。以便考览。以比子张书绅之意。而兼与二三同志后生共之。而时未暇耳。但恐兄力攻朱训。以为不足法也。鄙人尝以是奉规于吾兄。而兄以鄙说。比之于白昼执人。诬以杀人之类矣。今承来书。责鄙人曰。其于朱训。多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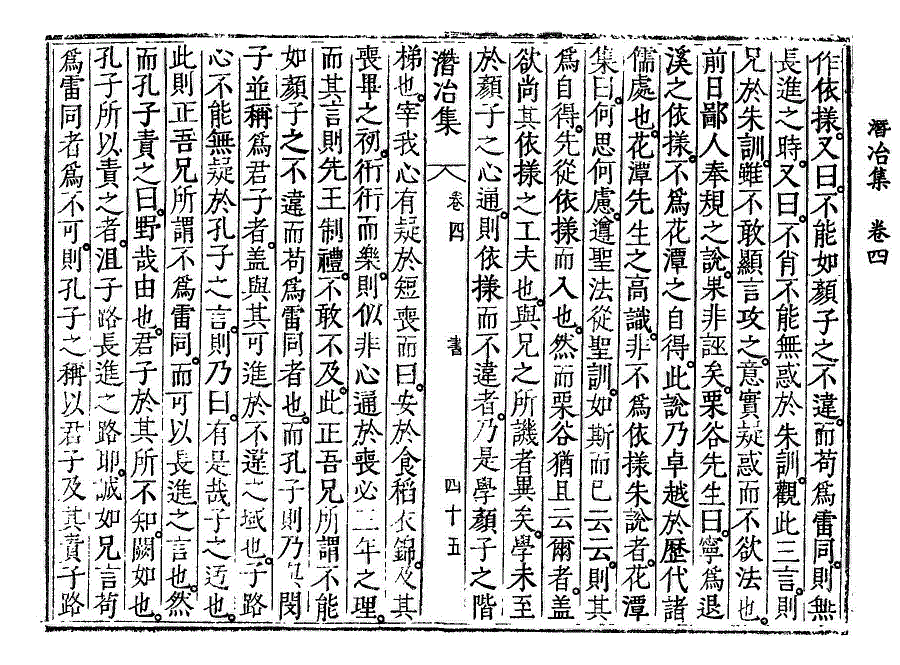 作依样。又曰。不能如颜子之不违。而苟为雷同。则无长进之时。又曰。不肖不能无惑于朱训。观此三言。则兄于朱训。虽不敢显言攻之。意实疑惑而不欲法也。前日鄙人奉规之说。果非诬矣。栗谷先生曰。宁为退溪之依样。不为花潭之自得。此说乃卓越于历代诸儒处也。花潭先生之高识。非不为依样朱说者。花潭集曰。何思何虑。遵圣法从圣训。如斯而已云云。则其为自得。先从依样而入也。然而栗谷犹且云尔者。盖欲尚其依样之工夫也。与兄之所讥者异矣。学未至于颜子之心通。则依样而不违者。乃是学颜子之阶梯也。宰我心有疑于短丧而曰。安于食稻衣锦。及其丧毕之初。衎衎而乐。则似非心通于丧必三年之理。而其言则先王制礼。不敢不及。此正吾兄所谓不能如颜子之不违而苟为雷同者也。而孔子则乃与闵子并称为君子者。盖与其可进于不违之域也。子路心不能无疑于孔子之言。则乃曰。有是哉子之迂也。此则正吾兄所谓不为雷同。而可以长进之言也。然而孔子责之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阙如也。孔子所以责之者。沮子路长进之路耶。诚如兄言苟为雷同者为不可。则孔子之称以君子及其责子路
作依样。又曰。不能如颜子之不违。而苟为雷同。则无长进之时。又曰。不肖不能无惑于朱训。观此三言。则兄于朱训。虽不敢显言攻之。意实疑惑而不欲法也。前日鄙人奉规之说。果非诬矣。栗谷先生曰。宁为退溪之依样。不为花潭之自得。此说乃卓越于历代诸儒处也。花潭先生之高识。非不为依样朱说者。花潭集曰。何思何虑。遵圣法从圣训。如斯而已云云。则其为自得。先从依样而入也。然而栗谷犹且云尔者。盖欲尚其依样之工夫也。与兄之所讥者异矣。学未至于颜子之心通。则依样而不违者。乃是学颜子之阶梯也。宰我心有疑于短丧而曰。安于食稻衣锦。及其丧毕之初。衎衎而乐。则似非心通于丧必三年之理。而其言则先王制礼。不敢不及。此正吾兄所谓不能如颜子之不违而苟为雷同者也。而孔子则乃与闵子并称为君子者。盖与其可进于不违之域也。子路心不能无疑于孔子之言。则乃曰。有是哉子之迂也。此则正吾兄所谓不为雷同。而可以长进之言也。然而孔子责之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阙如也。孔子所以责之者。沮子路长进之路耶。诚如兄言苟为雷同者为不可。则孔子之称以君子及其责子路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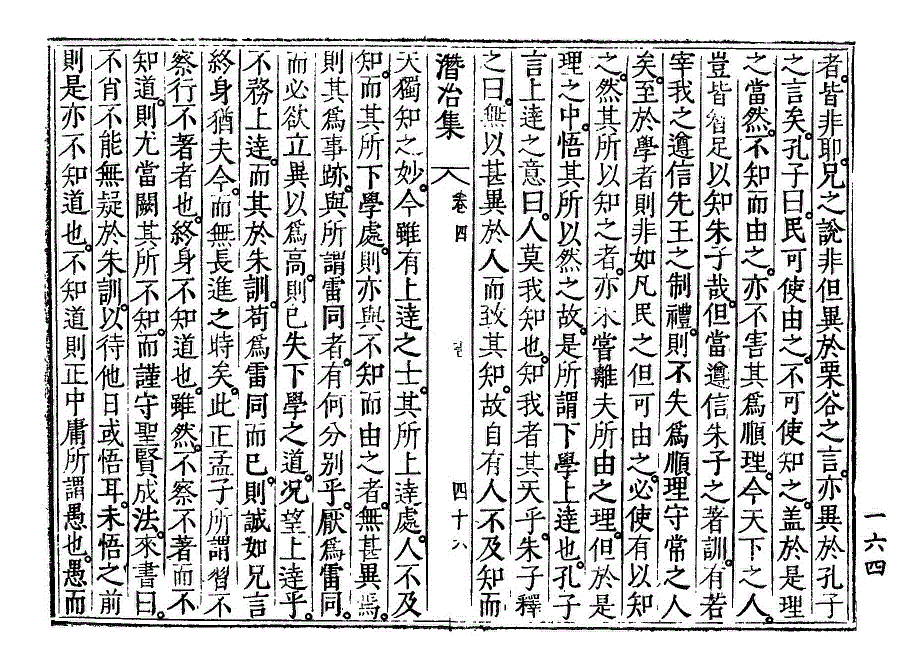 者。皆非耶。兄之说非但异于栗谷之言。亦异于孔子之言矣。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盖于是理之当然。不知而由之。亦不害其为顺理。今天下之人。岂皆智足以知朱子哉。但当遵信朱子之著训。有若宰我之遵信先王之制礼。则不失为顺理守常之人矣。至于学者则非如凡民之但可由之。必使有以知之。然其所以知之者。亦未尝离夫所由之理。但于是理之中。悟其所以然之故。是所谓下学上达也。孔子言上达之意曰。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朱子释之曰。无以甚异于人而致其知。故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独知之妙。今虽有上达之士。其所上达处。人不及知。而其所下学处。则亦与不知而由之者。无甚异焉。则其为事迹。与所谓雷同者。有何分别乎。厌为雷同。而必欲立异以为高。则已失下学之道。况望上达乎。不务上达。而其于朱训。苟为雷同而已。则诚如兄言终身犹夫今。而无长进之时矣。此正孟子所谓习不察行不著者也。终身不知道也。虽然。不察不著而不知道。则尤当阙其所不知。而谨守圣贤成法。来书曰。不肖不能无疑于朱训。以待他日或悟耳。未悟之前则是亦不知道也。不知道则正中庸所谓愚也。愚而
者。皆非耶。兄之说非但异于栗谷之言。亦异于孔子之言矣。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盖于是理之当然。不知而由之。亦不害其为顺理。今天下之人。岂皆智足以知朱子哉。但当遵信朱子之著训。有若宰我之遵信先王之制礼。则不失为顺理守常之人矣。至于学者则非如凡民之但可由之。必使有以知之。然其所以知之者。亦未尝离夫所由之理。但于是理之中。悟其所以然之故。是所谓下学上达也。孔子言上达之意曰。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朱子释之曰。无以甚异于人而致其知。故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独知之妙。今虽有上达之士。其所上达处。人不及知。而其所下学处。则亦与不知而由之者。无甚异焉。则其为事迹。与所谓雷同者。有何分别乎。厌为雷同。而必欲立异以为高。则已失下学之道。况望上达乎。不务上达。而其于朱训。苟为雷同而已。则诚如兄言终身犹夫今。而无长进之时矣。此正孟子所谓习不察行不著者也。终身不知道也。虽然。不察不著而不知道。则尤当阙其所不知。而谨守圣贤成法。来书曰。不肖不能无疑于朱训。以待他日或悟耳。未悟之前则是亦不知道也。不知道则正中庸所谓愚也。愚而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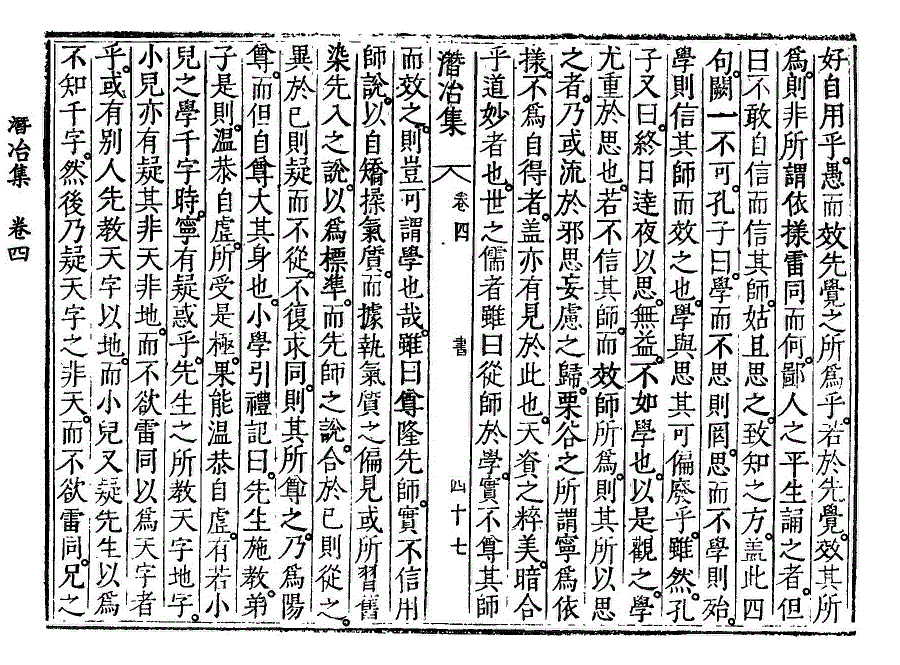 好自用乎。愚而效先觉之所为乎。若于先觉。效其所为。则非所谓依样雷同而何。鄙人之平生诵之者。但曰不敢自信而信其师。姑且思之。致知之方。盖此四句。阙一不可。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则信其师而效之也。学与思其可偏废乎。虽然。孔子又曰。终日达夜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以是观之。学尤重于思也。若不信其师。而效师所为。则其所以思之者。乃或流于邪思妄虑之归。栗谷之所谓宁为依样。不为自得者。盖亦有见于此也。天资之粹美。暗合乎道妙者也。世之儒者虽曰从师于学。实不尊其师而效之。则岂可谓学也哉。虽曰尊隆先师。实不信用师说。以自矫揉气质。而据执气质之偏见或所习旧染先入之说。以为标准。而先师之说。合于己则从之。异于己则疑而不从。不复求同。则其所尊之。乃为阳尊。而但自尊大其身也。小学引礼记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果能温恭自虚。有若小儿之学千字时。宁有疑或乎。先生之所教天字地字。小儿亦有疑其非天非地。而不欲雷同以为天字者乎。或有别人先教天字以地。而小儿又疑先生以为不知千字。然后乃疑天字之非天。而不欲雷同。兄之
好自用乎。愚而效先觉之所为乎。若于先觉。效其所为。则非所谓依样雷同而何。鄙人之平生诵之者。但曰不敢自信而信其师。姑且思之。致知之方。盖此四句。阙一不可。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则信其师而效之也。学与思其可偏废乎。虽然。孔子又曰。终日达夜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以是观之。学尤重于思也。若不信其师。而效师所为。则其所以思之者。乃或流于邪思妄虑之归。栗谷之所谓宁为依样。不为自得者。盖亦有见于此也。天资之粹美。暗合乎道妙者也。世之儒者虽曰从师于学。实不尊其师而效之。则岂可谓学也哉。虽曰尊隆先师。实不信用师说。以自矫揉气质。而据执气质之偏见或所习旧染先入之说。以为标准。而先师之说。合于己则从之。异于己则疑而不从。不复求同。则其所尊之。乃为阳尊。而但自尊大其身也。小学引礼记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果能温恭自虚。有若小儿之学千字时。宁有疑或乎。先生之所教天字地字。小儿亦有疑其非天非地。而不欲雷同以为天字者乎。或有别人先教天字以地。而小儿又疑先生以为不知千字。然后乃疑天字之非天。而不欲雷同。兄之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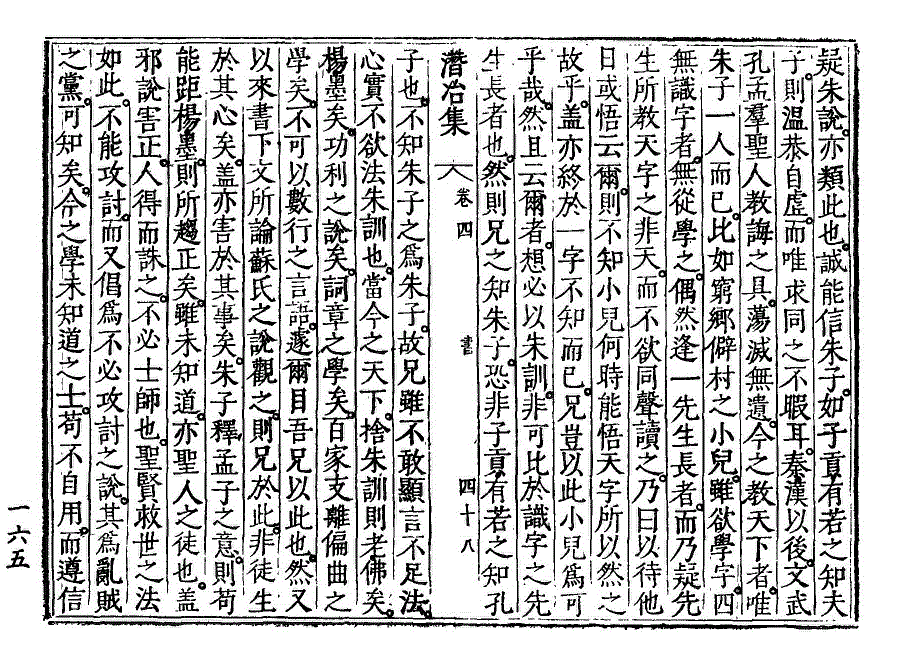 疑朱说。亦类此也。诚能信朱子。如子贡,有若之知夫子。则温恭自虚。而唯求同之不暇耳。秦,汉以后。文武孔孟群圣人教诲之具。荡灭无遗。今之教天下者。唯朱子一人而已。比如穷乡僻村之小儿。虽欲学字。四无识字者。无从学之。偶然逢一先生长者。而乃疑先生所教天字之非天。而不欲同声读之。乃曰以待他日或悟云尔。则不知小儿何时能悟天字所以然之故乎。盖亦终于一字不知而己。兄岂以此小儿为可乎哉。然且云尔者。想必以朱训。非可比于识字之先生长者也。然则兄之知朱子。恐非子贡,有若之知孔子也。不知朱子之为朱子。故兄虽不敢显言不足法。心实不欲法朱训也。当今之天下。舍朱训则老,佛矣。杨,墨矣。功利之说矣。词章之学矣。百家支离偏曲之学矣。不可以数行之言语。遽尔目吾兄以此也。然又以来书下文所论苏氏之说观之。则兄于此。非徒生于其心矣。盖亦害于其事矣。朱子释孟子之意。则苟能距杨,墨。则所趋正矣。虽未知道。亦圣人之徒也。盖邪说害正。人得而诛之。不必士师也。圣贤救世之法如此。不能攻讨。而又倡为不必攻讨之说。其为乱贼之党。可知矣。今之学未知道之士。苟不自用。而遵信
疑朱说。亦类此也。诚能信朱子。如子贡,有若之知夫子。则温恭自虚。而唯求同之不暇耳。秦,汉以后。文武孔孟群圣人教诲之具。荡灭无遗。今之教天下者。唯朱子一人而已。比如穷乡僻村之小儿。虽欲学字。四无识字者。无从学之。偶然逢一先生长者。而乃疑先生所教天字之非天。而不欲同声读之。乃曰以待他日或悟云尔。则不知小儿何时能悟天字所以然之故乎。盖亦终于一字不知而己。兄岂以此小儿为可乎哉。然且云尔者。想必以朱训。非可比于识字之先生长者也。然则兄之知朱子。恐非子贡,有若之知孔子也。不知朱子之为朱子。故兄虽不敢显言不足法。心实不欲法朱训也。当今之天下。舍朱训则老,佛矣。杨,墨矣。功利之说矣。词章之学矣。百家支离偏曲之学矣。不可以数行之言语。遽尔目吾兄以此也。然又以来书下文所论苏氏之说观之。则兄于此。非徒生于其心矣。盖亦害于其事矣。朱子释孟子之意。则苟能距杨,墨。则所趋正矣。虽未知道。亦圣人之徒也。盖邪说害正。人得而诛之。不必士师也。圣贤救世之法如此。不能攻讨。而又倡为不必攻讨之说。其为乱贼之党。可知矣。今之学未知道之士。苟不自用。而遵信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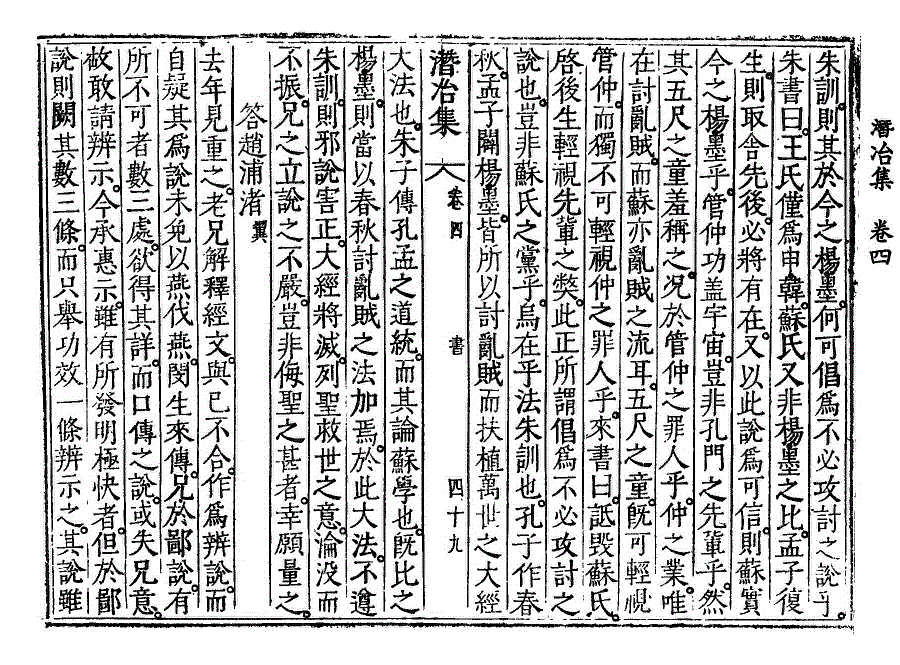 朱训。则其于今之杨,墨。何可倡为不必攻讨之说乎。朱书曰。王氏仅为申,韩。苏氏又非杨,墨之比。孟子复生。则取舍先后。必将有在。又以此说为可信。则苏实今之杨,墨乎。管仲功盖宇宙。岂非孔门之先辈乎。然其五尺之童羞称之。况于管仲之罪人乎。仲之业。唯在讨乱贼。而苏亦乱贼之流耳。五尺之童。既可轻视管仲。而独不可轻视仲之罪人乎。来书曰。诋毁苏氏。启后生轻视先辈之弊。此正所谓倡为不必攻讨之说也。岂非苏氏之党乎。乌在乎法朱训也。孔子作春秋。孟子辟杨,墨。皆所以讨乱贼而扶植万世之大经大法也。朱子传孔孟之道统。而其论苏学也。既比之杨,墨。当则以春秋讨乱贼之法加焉。于此大法。不遵朱训。则邪说害正。大经将灭。列圣救世之意。沦没而不振。兄之立说之不严。岂非侮圣之甚者。幸愿量之。
朱训。则其于今之杨,墨。何可倡为不必攻讨之说乎。朱书曰。王氏仅为申,韩。苏氏又非杨,墨之比。孟子复生。则取舍先后。必将有在。又以此说为可信。则苏实今之杨,墨乎。管仲功盖宇宙。岂非孔门之先辈乎。然其五尺之童羞称之。况于管仲之罪人乎。仲之业。唯在讨乱贼。而苏亦乱贼之流耳。五尺之童。既可轻视管仲。而独不可轻视仲之罪人乎。来书曰。诋毁苏氏。启后生轻视先辈之弊。此正所谓倡为不必攻讨之说也。岂非苏氏之党乎。乌在乎法朱训也。孔子作春秋。孟子辟杨,墨。皆所以讨乱贼而扶植万世之大经大法也。朱子传孔孟之道统。而其论苏学也。既比之杨,墨。当则以春秋讨乱贼之法加焉。于此大法。不遵朱训。则邪说害正。大经将灭。列圣救世之意。沦没而不振。兄之立说之不严。岂非侮圣之甚者。幸愿量之。答赵浦渚(翼)
去年见重之。老兄解释经文。与己不合。作为辨说。而自疑其为说未免以燕伐燕。闵生来传。兄于鄙说。有所不可者数三处。欲得其详。而口传之说。或失兄意。故敢请辨示。今承惠示。虽有所发明极快者。但于鄙说则阙其数三条。而只举功效一条辨示之。其说虽
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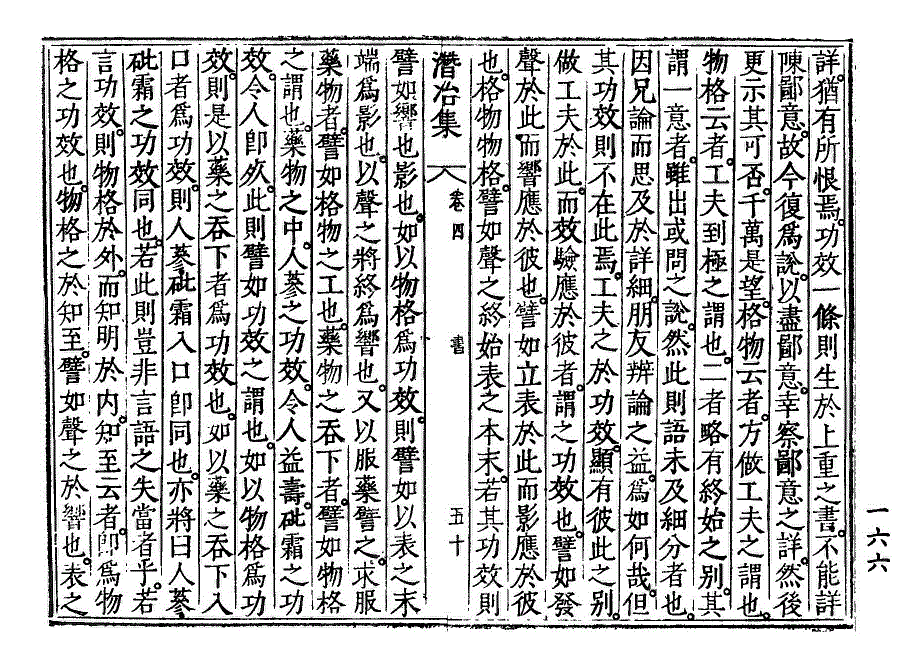 详。犹有所恨焉。功效一条则生于上重之书。不能详陈鄙意。故今复为说。以尽鄙意。幸察鄙意之详。然后更示其可否。千万是望。格物云者。方做工夫之谓也。物格云者。工夫到极之谓也。二者略有终始之别。其谓一意者。虽出或问之说。然此则语未及细分者也。因兄论而思及于详细。朋友辨论之益。为如何哉。但其功效则不在此焉。工夫之于功效。显有从此之别。做工夫于此。而效验应于彼者。谓之功效也。譬如发声于此而响应于彼也。譬如立表于此而影应于彼也。格物物格。譬如声之终始表之本末。若其功效则譬如响也影也。如以物格为功效。则譬如以表之末端为影也。以声之将终为响也。又以服药譬之。求服药物者。譬如格物之工也。药物之吞下者。譬如物格之谓也。药物之中。人蔘之功效。令人益寿。砒霜之功效。令人即死。此则譬如功效之谓也。如以物格为功效。则是以药之吞下者为功效也。如以药之吞下入口者为功效。则人蔘,砒霜入口即同也。亦将曰人蔘,砒霜之功效同也。若此则岂非言语之失当者乎。若言功效。则物格于外。而知明于内。知至云者。即为物格之功效也。物格之于知至。譬如声之于响也。表之
详。犹有所恨焉。功效一条则生于上重之书。不能详陈鄙意。故今复为说。以尽鄙意。幸察鄙意之详。然后更示其可否。千万是望。格物云者。方做工夫之谓也。物格云者。工夫到极之谓也。二者略有终始之别。其谓一意者。虽出或问之说。然此则语未及细分者也。因兄论而思及于详细。朋友辨论之益。为如何哉。但其功效则不在此焉。工夫之于功效。显有从此之别。做工夫于此。而效验应于彼者。谓之功效也。譬如发声于此而响应于彼也。譬如立表于此而影应于彼也。格物物格。譬如声之终始表之本末。若其功效则譬如响也影也。如以物格为功效。则譬如以表之末端为影也。以声之将终为响也。又以服药譬之。求服药物者。譬如格物之工也。药物之吞下者。譬如物格之谓也。药物之中。人蔘之功效。令人益寿。砒霜之功效。令人即死。此则譬如功效之谓也。如以物格为功效。则是以药之吞下者为功效也。如以药之吞下入口者为功效。则人蔘,砒霜入口即同也。亦将曰人蔘,砒霜之功效同也。若此则岂非言语之失当者乎。若言功效。则物格于外。而知明于内。知至云者。即为物格之功效也。物格之于知至。譬如声之于响也。表之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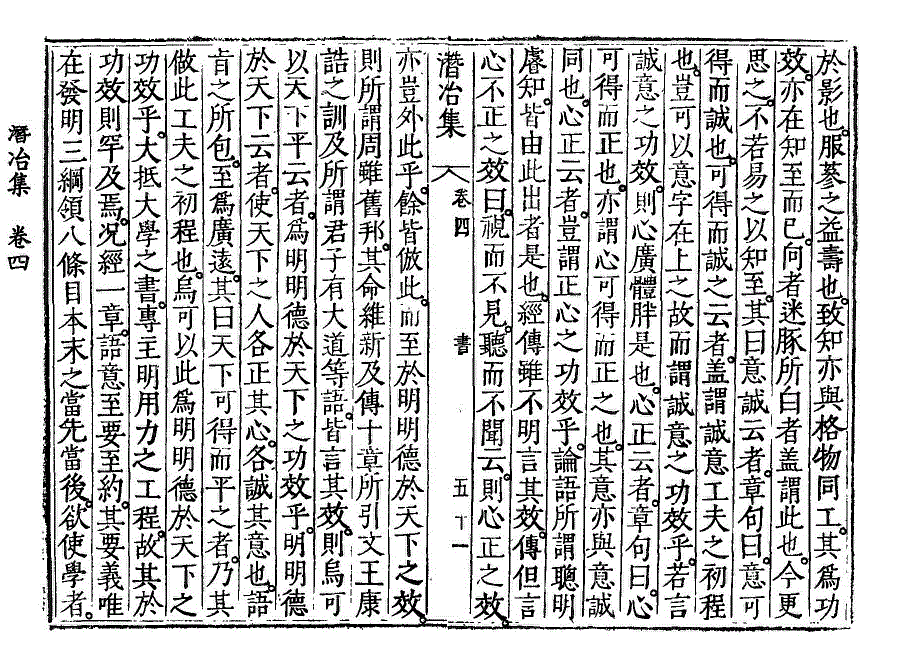 于影也。服蔘之益寿也。致知亦与格物同工。其为功效。亦在知至而已。向者迷豚所白者盖谓此也。今更思之。不若易之以知至。其曰意诚云者。章句曰。意可得而诚也。可得而诚之云者。盖谓诚意工夫之初程也。岂可以意字在上之故而谓诚意之功效乎。若言诚意之功效。则心广体胖是也。心正云者。章句曰。心可得而正也。亦谓心可得而正之也。其意亦与意诚同也。心正云者。岂谓正心之功效乎。论语所谓聪明睿知。皆由此出者是也。经传虽不明言其效。传但言心不正之效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云。则心正之效。亦岂外此乎。馀皆仿此。而至于明明德于天下之效。则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及传十章所引文王康诰之训及所谓君子有大道等语。皆言其效。则乌可以天下平云者。为明明德于天下之功效乎。明明德于天下云者。使天下之人各正其心。各诚其意也。语旨之所包。至为广远。其曰天下可得而平之者。乃其做此工夫之初程也。乌可以此为明明德于天下之功效乎。大抵大学之书。专主明用力之工程。故其于功效则罕及焉。况经一章。语意至要至约。其要义唯在发明三纲领八条目本末之当先当后。欲使学者。
于影也。服蔘之益寿也。致知亦与格物同工。其为功效。亦在知至而已。向者迷豚所白者盖谓此也。今更思之。不若易之以知至。其曰意诚云者。章句曰。意可得而诚也。可得而诚之云者。盖谓诚意工夫之初程也。岂可以意字在上之故而谓诚意之功效乎。若言诚意之功效。则心广体胖是也。心正云者。章句曰。心可得而正也。亦谓心可得而正之也。其意亦与意诚同也。心正云者。岂谓正心之功效乎。论语所谓聪明睿知。皆由此出者是也。经传虽不明言其效。传但言心不正之效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云。则心正之效。亦岂外此乎。馀皆仿此。而至于明明德于天下之效。则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及传十章所引文王康诰之训及所谓君子有大道等语。皆言其效。则乌可以天下平云者。为明明德于天下之功效乎。明明德于天下云者。使天下之人各正其心。各诚其意也。语旨之所包。至为广远。其曰天下可得而平之者。乃其做此工夫之初程也。乌可以此为明明德于天下之功效乎。大抵大学之书。专主明用力之工程。故其于功效则罕及焉。况经一章。语意至要至约。其要义唯在发明三纲领八条目本末之当先当后。欲使学者。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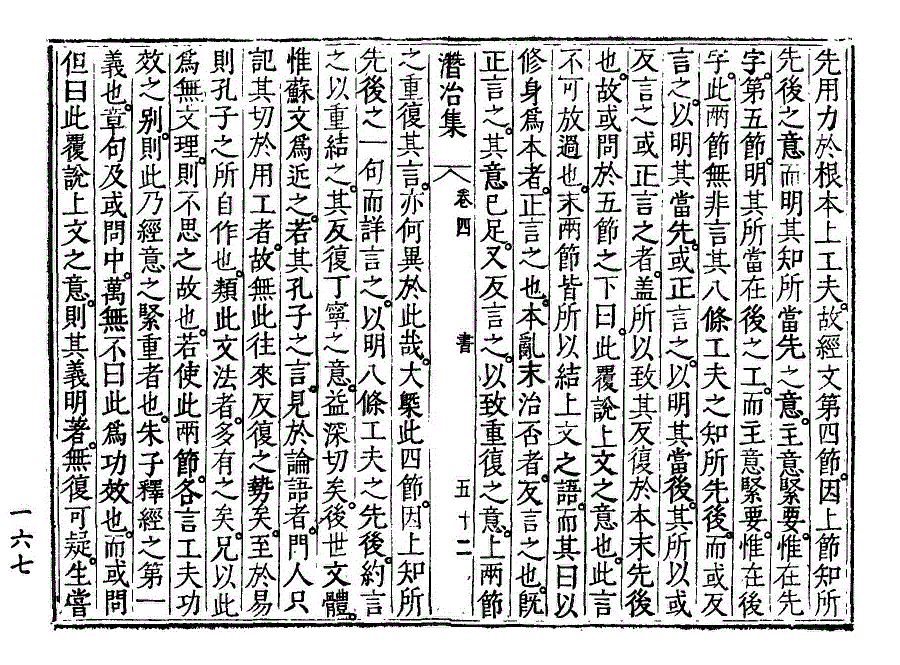 先用力于根本上工夫。故经文第四节。因上节知所先后之意而明其知所当先之意。主意紧要。惟在先字。第五节。明其所当在后之工。而主意紧要。惟在后字。此两节无非言其八条工夫之知所先后。而或反言之。以明其当先。或正言之。以明其当后。其所以或反言之或正言之者。盖所以致其反复于本末先后也。故或问于五节之下曰。此覆说上文之意也。此言不可放过也。末两节皆所以结上文之语。而其曰以修身为本者。正言之也。本乱末治否者。反言之也。既正言之。其意已足。又反言之。以致重复之意。上两节之重复其言。亦何异于此哉。大槩此四节。因上知所先后之一句而详言之。以明八条工夫之先后。约言之以重结之。其反复丁宁之意。益深切矣。后世文体。惟苏文为近之。若其孔子之言。见于论语者。门人只记其切于用工者。故无此往来反复之势矣。至于易则孔子之所自作也。类此文法者。多有之矣。兄以此为无文理。则不思之故也。若使此两节。各言工夫功效之别。则此乃经意之紧重者也。朱子释经之第一义也。章句及或问中。万无不曰此为功效也。而或问但曰此覆说上文之意。则其义明著。无复可疑。生尝
先用力于根本上工夫。故经文第四节。因上节知所先后之意而明其知所当先之意。主意紧要。惟在先字。第五节。明其所当在后之工。而主意紧要。惟在后字。此两节无非言其八条工夫之知所先后。而或反言之。以明其当先。或正言之。以明其当后。其所以或反言之或正言之者。盖所以致其反复于本末先后也。故或问于五节之下曰。此覆说上文之意也。此言不可放过也。末两节皆所以结上文之语。而其曰以修身为本者。正言之也。本乱末治否者。反言之也。既正言之。其意已足。又反言之。以致重复之意。上两节之重复其言。亦何异于此哉。大槩此四节。因上知所先后之一句而详言之。以明八条工夫之先后。约言之以重结之。其反复丁宁之意。益深切矣。后世文体。惟苏文为近之。若其孔子之言。见于论语者。门人只记其切于用工者。故无此往来反复之势矣。至于易则孔子之所自作也。类此文法者。多有之矣。兄以此为无文理。则不思之故也。若使此两节。各言工夫功效之别。则此乃经意之紧重者也。朱子释经之第一义也。章句及或问中。万无不曰此为功效也。而或问但曰此覆说上文之意。则其义明著。无复可疑。生尝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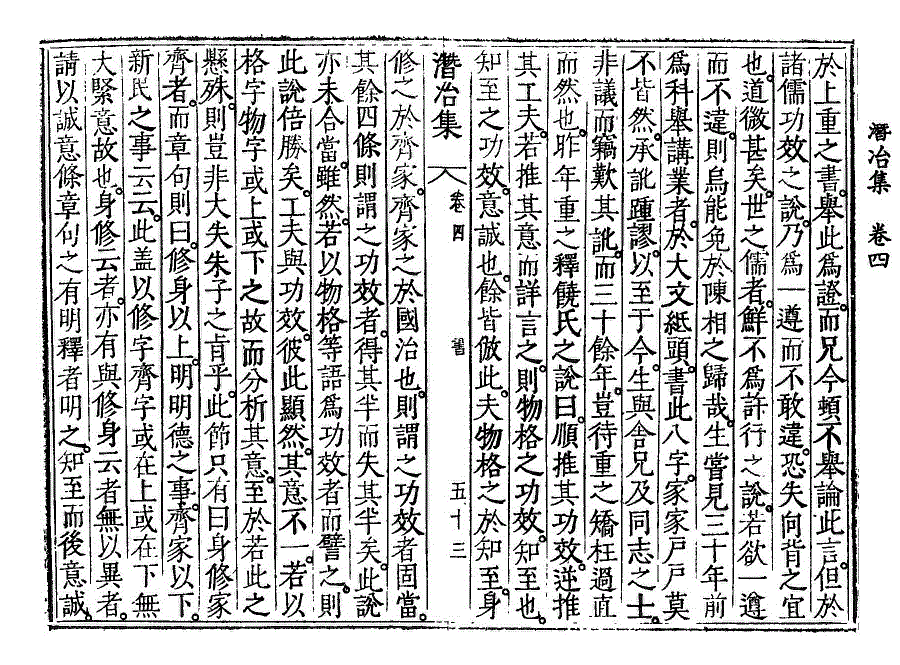 于上重之书。举此为證。而兄今顿不举论此言。但于诸儒功效之说。乃为一遵而不敢违。恐失向背之宜也。道微甚矣。世之儒者。鲜不为许行之说。若欲一遵而不违。则乌能免于陈相之归哉。生尝见三十年前为科举讲业者。于大文纸头。书此八字。家家户户莫不皆然。承讹踵谬。以至于今。生与舍兄及同志之士。非议而窃叹其讹。而三十馀年。岂待重之矫枉过直而然也。昨年重之释饶氏之说曰。顺推其功效。逆推其工夫。若推其意而详言之。则物格之功效。知至也。知至之功效。意诚也。馀皆仿此。夫物格之于知至。身修之于齐家。齐家之于国治也。则谓之功效者固当。其馀四条则谓之功效者。得其半而失其半矣。此说亦未合当。虽然。若以物格等语为功效者而譬之。则此说倍胜矣。工夫与功效。彼此显然。其意不一。若以格字物字或上或下之故而分析其意。至于若此之悬殊。则岂非大失朱子之旨乎。此节只有曰身修家齐者。而章句则曰。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云云。此盖以修字齐字或在上或在下无大紧意故也。身修云者。亦有与修身云者无以异者。请以诚意条章句之有明释者明之。知至而后意诚。
于上重之书。举此为證。而兄今顿不举论此言。但于诸儒功效之说。乃为一遵而不敢违。恐失向背之宜也。道微甚矣。世之儒者。鲜不为许行之说。若欲一遵而不违。则乌能免于陈相之归哉。生尝见三十年前为科举讲业者。于大文纸头。书此八字。家家户户莫不皆然。承讹踵谬。以至于今。生与舍兄及同志之士。非议而窃叹其讹。而三十馀年。岂待重之矫枉过直而然也。昨年重之释饶氏之说曰。顺推其功效。逆推其工夫。若推其意而详言之。则物格之功效。知至也。知至之功效。意诚也。馀皆仿此。夫物格之于知至。身修之于齐家。齐家之于国治也。则谓之功效者固当。其馀四条则谓之功效者。得其半而失其半矣。此说亦未合当。虽然。若以物格等语为功效者而譬之。则此说倍胜矣。工夫与功效。彼此显然。其意不一。若以格字物字或上或下之故而分析其意。至于若此之悬殊。则岂非大失朱子之旨乎。此节只有曰身修家齐者。而章句则曰。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云云。此盖以修字齐字或在上或在下无大紧意故也。身修云者。亦有与修身云者无以异者。请以诚意条章句之有明释者明之。知至而后意诚。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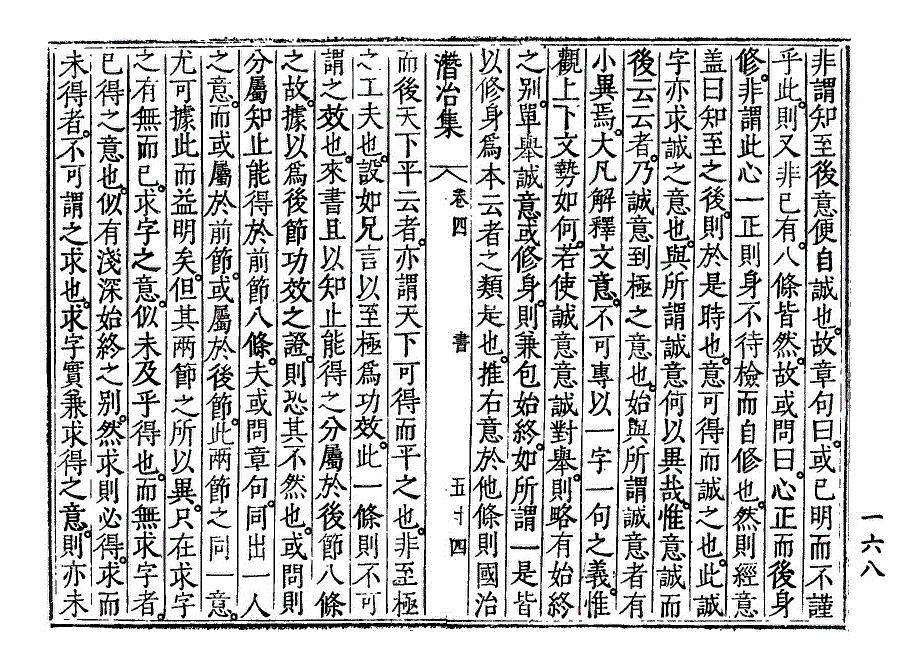 非谓知至后意便自诚也。故章句曰。或已明而不谨乎此。则又非己有。八条皆然。故或问曰。心正而后身修。非谓此心一正则身不待检而自修也。然则经意盖曰知至之后。则于是时也。意可得而诚之也。此诚字亦求诚之意也。与所谓诚意何以异哉。惟意诚而后云云者。乃诚意到极之意也。始与所谓诚意者有小异焉。大凡解释文意。不可专以一字一句之义。惟观上下文势如何。若使诚意意诚对举。则略有始终之别。单举诚意或修身。则兼包始终。如所谓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云者之类是也。推右意于他条则国治而后天下平云者。亦谓天下可得而平之也。非至极之工夫也。设如兄言以至极为功效。此一条则不可谓之效也。来书且以知止能得之分属于后节八条之故。据以为后节功效之證。则恐其不然也。或问则分属知止能得于前节八条。夫或问章句。同出一人之意。而或属于前节。或属于后节。此两节之同一意。尤可据此而益明矣。但其两节之所以异。只在求字之有无而已。求字之意。似未及乎得也。而无求字者。已得之意也。似有浅深始终之别。然求则必得。求而未得者。不可谓之求也。求字实兼求得之意。则亦未
非谓知至后意便自诚也。故章句曰。或已明而不谨乎此。则又非己有。八条皆然。故或问曰。心正而后身修。非谓此心一正则身不待检而自修也。然则经意盖曰知至之后。则于是时也。意可得而诚之也。此诚字亦求诚之意也。与所谓诚意何以异哉。惟意诚而后云云者。乃诚意到极之意也。始与所谓诚意者有小异焉。大凡解释文意。不可专以一字一句之义。惟观上下文势如何。若使诚意意诚对举。则略有始终之别。单举诚意或修身。则兼包始终。如所谓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云者之类是也。推右意于他条则国治而后天下平云者。亦谓天下可得而平之也。非至极之工夫也。设如兄言以至极为功效。此一条则不可谓之效也。来书且以知止能得之分属于后节八条之故。据以为后节功效之證。则恐其不然也。或问则分属知止能得于前节八条。夫或问章句。同出一人之意。而或属于前节。或属于后节。此两节之同一意。尤可据此而益明矣。但其两节之所以异。只在求字之有无而已。求字之意。似未及乎得也。而无求字者。已得之意也。似有浅深始终之别。然求则必得。求而未得者。不可谓之求也。求字实兼求得之意。则亦未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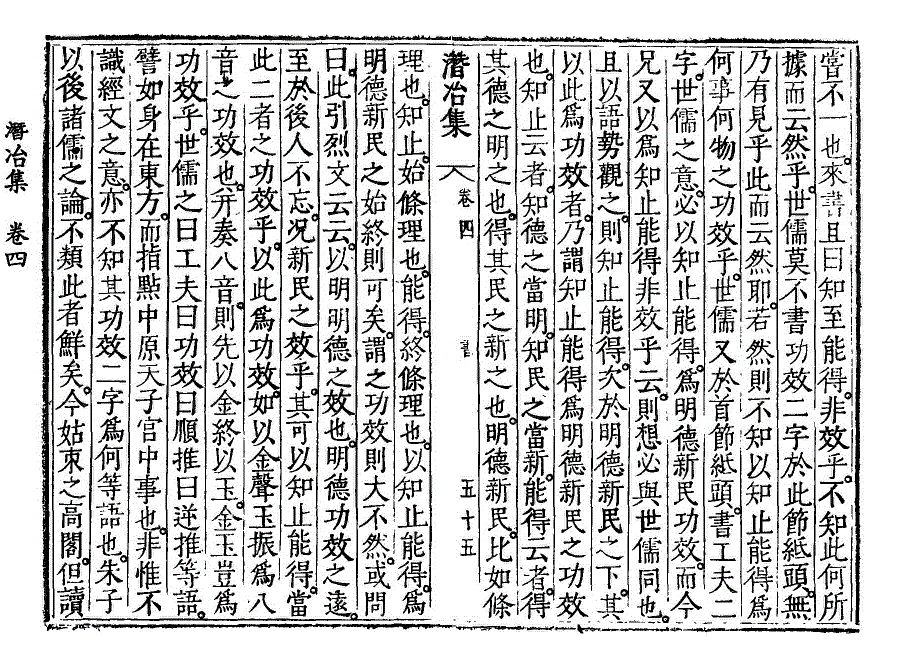 尝不一也。来书且曰知至能得。非效乎。不知此何所据而云然乎。世儒莫不书功效二字于此节纸头。无乃有见乎此而云然耶。若然则不知以知止能得为何事何物之功效乎。世儒又于首节纸头。书工夫二字。世儒之意。必以知止能得。为明德新民功效。而今兄又以为知止能得非效乎云。则想必与世儒同也。且以语势观之。则知止能得。次于明德新民之下。其以此为功效者。乃谓知止能得为明德新民之功效也。知止云者。知德之当明。知民之当新。能得云者。得其德之明之也。得其民之新之也。明德新民。比如条理也。知止。始条理也。能得。终条理也。以知止能得。为明德新民之始终则可矣。谓之功效则大不然。或问曰。此引烈文云云。以明明德之效也。明德功效之远。至于后人不忘。况新民之效乎。其可以知止能得。当此二者之功效乎。以此为功效。如以金声玉振为八音之功效也。并奏八音。则先以金终以玉。金玉岂为功效乎。世儒之曰工夫曰功效曰顺推曰逆推等语。譬如身在东方。而指点中原天子宫中事也。非惟不识经文之意。亦不知其功效二字为何等语也。朱子以后诸儒之论。不类此者鲜矣。今姑束之高阁。但读
尝不一也。来书且曰知至能得。非效乎。不知此何所据而云然乎。世儒莫不书功效二字于此节纸头。无乃有见乎此而云然耶。若然则不知以知止能得为何事何物之功效乎。世儒又于首节纸头。书工夫二字。世儒之意。必以知止能得。为明德新民功效。而今兄又以为知止能得非效乎云。则想必与世儒同也。且以语势观之。则知止能得。次于明德新民之下。其以此为功效者。乃谓知止能得为明德新民之功效也。知止云者。知德之当明。知民之当新。能得云者。得其德之明之也。得其民之新之也。明德新民。比如条理也。知止。始条理也。能得。终条理也。以知止能得。为明德新民之始终则可矣。谓之功效则大不然。或问曰。此引烈文云云。以明明德之效也。明德功效之远。至于后人不忘。况新民之效乎。其可以知止能得。当此二者之功效乎。以此为功效。如以金声玉振为八音之功效也。并奏八音。则先以金终以玉。金玉岂为功效乎。世儒之曰工夫曰功效曰顺推曰逆推等语。譬如身在东方。而指点中原天子宫中事也。非惟不识经文之意。亦不知其功效二字为何等语也。朱子以后诸儒之论。不类此者鲜矣。今姑束之高阁。但读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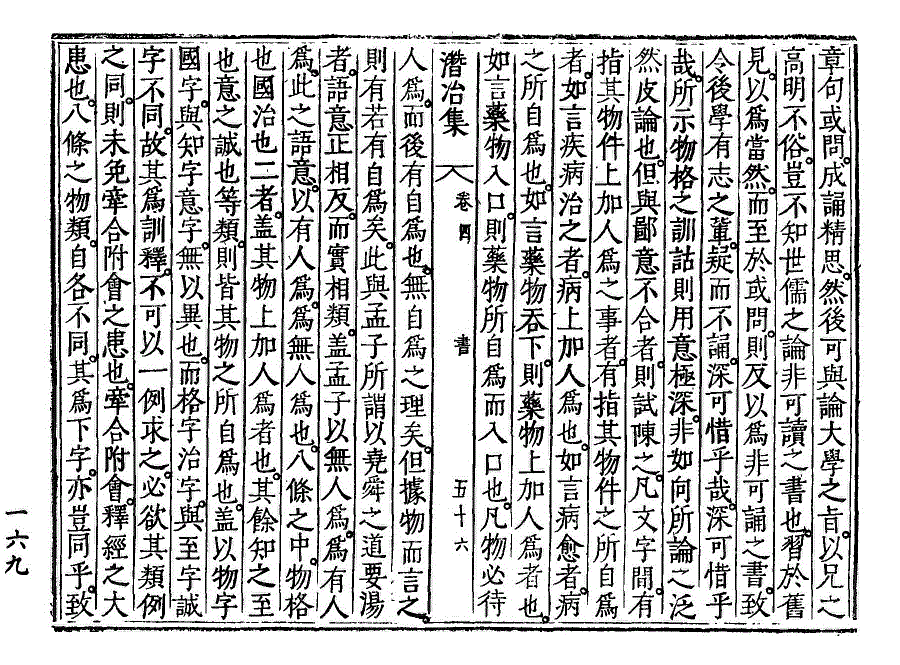 章句或问。成诵精思。然后可与论大学之旨。以兄之高明不俗。岂不知世儒之论非可读之书也。习于旧见。以为当然。而至于或问。则反以为非可诵之书。致令后学有志之辈。疑而不诵。深可惜乎哉。深可惜乎哉。所示物格之训诂则用意极深。非如向所论之泛然皮论也。但与鄙意不合者。则试陈之。凡文字间。有指其物件上加人为之事者。有指其物件之所自为者。如言疾病治之者。病上加人为也。如言病愈者。病之所自为也。如言药物吞下。则药物上加人为者也。如言药物入口。则药物所自为而入口也。凡物必待人为。而后有自为也。无自为之理矣。但据物而言之。则有若有自为矣。此与孟子所谓以尧舜之道要汤者。语意正相反。而实相类。盖孟子以无人为。为有人为。此之语意。以有人为。为无人为也。八条之中。物格也国治也二者。盖其物上加人为者也。其馀知之至也意之诚也等类。则皆其物之所自为也。盖以物字国字。与知字意字。无以异也。而格字治字。与至字诚字不同。故其为训释。不可以一例求之。必欲其类例之同。则未免牵合附会之患也。牵合附会。释经之大患也。八条之物类。自各不同。其为下字。亦岂同乎。致
章句或问。成诵精思。然后可与论大学之旨。以兄之高明不俗。岂不知世儒之论非可读之书也。习于旧见。以为当然。而至于或问。则反以为非可诵之书。致令后学有志之辈。疑而不诵。深可惜乎哉。深可惜乎哉。所示物格之训诂则用意极深。非如向所论之泛然皮论也。但与鄙意不合者。则试陈之。凡文字间。有指其物件上加人为之事者。有指其物件之所自为者。如言疾病治之者。病上加人为也。如言病愈者。病之所自为也。如言药物吞下。则药物上加人为者也。如言药物入口。则药物所自为而入口也。凡物必待人为。而后有自为也。无自为之理矣。但据物而言之。则有若有自为矣。此与孟子所谓以尧舜之道要汤者。语意正相反。而实相类。盖孟子以无人为。为有人为。此之语意。以有人为。为无人为也。八条之中。物格也国治也二者。盖其物上加人为者也。其馀知之至也意之诚也等类。则皆其物之所自为也。盖以物字国字。与知字意字。无以异也。而格字治字。与至字诚字不同。故其为训释。不可以一例求之。必欲其类例之同。则未免牵合附会之患也。牵合附会。释经之大患也。八条之物类。自各不同。其为下字。亦岂同乎。致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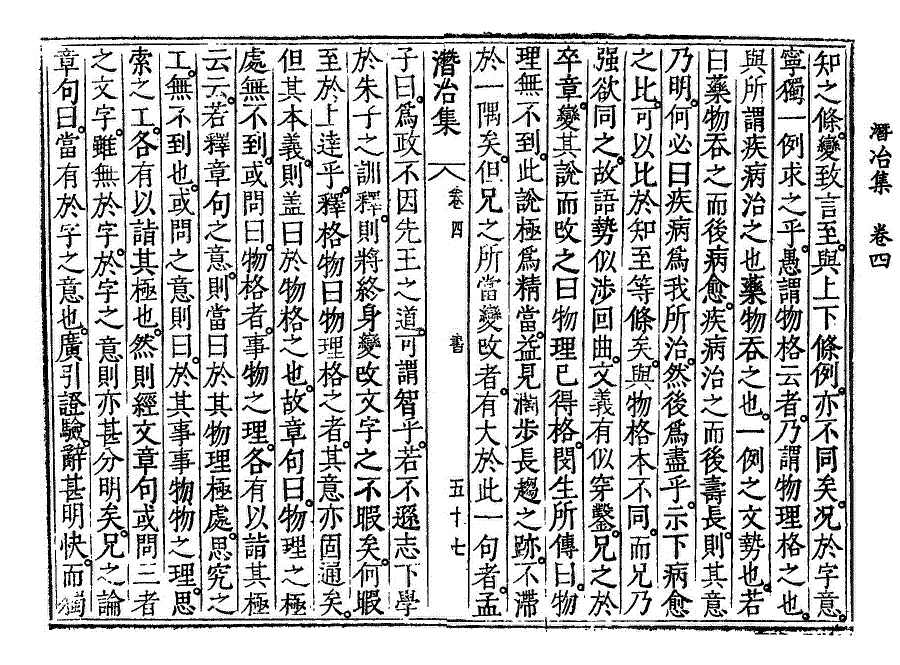 知之条。变致言至。与上下条例。亦不同矣。况于字意。宁独一例求之乎。愚谓物格云者。乃谓物理格之也。与所谓疾病治之也药物吞之也。一例之文势也。若曰药物吞之而后病愈。疾病治之而后寿长。则其意乃明。何必曰疾病为我所治。然后为尽乎。示下病愈之比。可以比于知至等条矣。与物格本不同。而兄乃强欲同之。故语势似涉回曲。文义有似穿凿。兄之于卒章。变其说而改之曰物理已得格。闵生所传曰。物理无不到。此说极为精当。益见阔步长趋之迹。不滞于一隅矣。但兄之所当变改者。有大于此一句者。孟子曰。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若不逊志下学于朱子之训释。则将终身变改文字之不暇矣。何暇至于上达乎。释格物曰物理格之者。其意亦固通矣。但其本义。则盖曰于物格之也。故章句曰。物理之极处无不到。或问曰。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诣其极云云。若释章句之意。则当曰于其物理极处。思究之工。无不到也。或问之意则曰。于其事事物物之理。思索之工。各有以诣其极也。然则经文章句或问三者之文字。虽无于字。于字之意则亦甚分明矣。兄之论章句曰。当有于字之意也。广引證验。辞甚明快。而独
知之条。变致言至。与上下条例。亦不同矣。况于字意。宁独一例求之乎。愚谓物格云者。乃谓物理格之也。与所谓疾病治之也药物吞之也。一例之文势也。若曰药物吞之而后病愈。疾病治之而后寿长。则其意乃明。何必曰疾病为我所治。然后为尽乎。示下病愈之比。可以比于知至等条矣。与物格本不同。而兄乃强欲同之。故语势似涉回曲。文义有似穿凿。兄之于卒章。变其说而改之曰物理已得格。闵生所传曰。物理无不到。此说极为精当。益见阔步长趋之迹。不滞于一隅矣。但兄之所当变改者。有大于此一句者。孟子曰。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若不逊志下学于朱子之训释。则将终身变改文字之不暇矣。何暇至于上达乎。释格物曰物理格之者。其意亦固通矣。但其本义。则盖曰于物格之也。故章句曰。物理之极处无不到。或问曰。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诣其极云云。若释章句之意。则当曰于其物理极处。思究之工。无不到也。或问之意则曰。于其事事物物之理。思索之工。各有以诣其极也。然则经文章句或问三者之文字。虽无于字。于字之意则亦甚分明矣。兄之论章句曰。当有于字之意也。广引證验。辞甚明快。而独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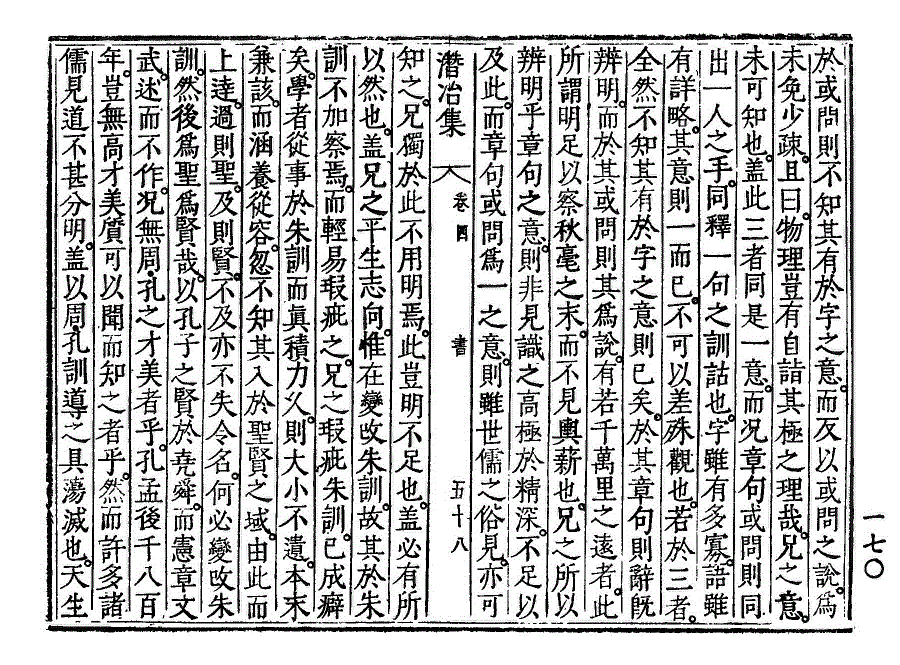 于或问则不知其有于字之意。而反以或问之说。为未免少疏。且曰。物理岂有自诣其极之理哉。兄之意。未可知也。盖此三者同是一意。而况章句或问则同出一人之手。同释一句之训诂也。字虽有多寡。语虽有详略。其意则一而已。不可以差殊观也。若于三者。全然不知其有于字之意则已矣。于其章句则辞既辨明。而于其或问则其为说。有若千万里之远者。此所谓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也。兄之所以辨明乎章句之意。则非见识之高极于精深。不足以及此。而章句或问为一之意。则虽世儒之俗见。亦可知之。兄独于此不用明焉。此岂明不足也。盖必有所以然也。盖兄之平生志向。惟在变改朱训。故其于朱训不加察焉。而轻易瑕疵之。兄之瑕疵朱训。已成癖矣。学者从事于朱训而真积力久。则大小不遗。本末兼该。而涵养从容。忽不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由此而上达。过则圣。及则贤。不及亦不失令名。何必变改朱训。然后为圣为贤哉。以孔子之贤于尧舜。而宪章文武。述而不作。况无周,孔之才美者乎。孔孟后千八百年。岂无高才美质可以闻而知之者乎。然而许多诸儒见道不甚分明。盖以周,孔训导之具荡灭也。天生
于或问则不知其有于字之意。而反以或问之说。为未免少疏。且曰。物理岂有自诣其极之理哉。兄之意。未可知也。盖此三者同是一意。而况章句或问则同出一人之手。同释一句之训诂也。字虽有多寡。语虽有详略。其意则一而已。不可以差殊观也。若于三者。全然不知其有于字之意则已矣。于其章句则辞既辨明。而于其或问则其为说。有若千万里之远者。此所谓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也。兄之所以辨明乎章句之意。则非见识之高极于精深。不足以及此。而章句或问为一之意。则虽世儒之俗见。亦可知之。兄独于此不用明焉。此岂明不足也。盖必有所以然也。盖兄之平生志向。惟在变改朱训。故其于朱训不加察焉。而轻易瑕疵之。兄之瑕疵朱训。已成癖矣。学者从事于朱训而真积力久。则大小不遗。本末兼该。而涵养从容。忽不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由此而上达。过则圣。及则贤。不及亦不失令名。何必变改朱训。然后为圣为贤哉。以孔子之贤于尧舜。而宪章文武。述而不作。况无周,孔之才美者乎。孔孟后千八百年。岂无高才美质可以闻而知之者乎。然而许多诸儒见道不甚分明。盖以周,孔训导之具荡灭也。天生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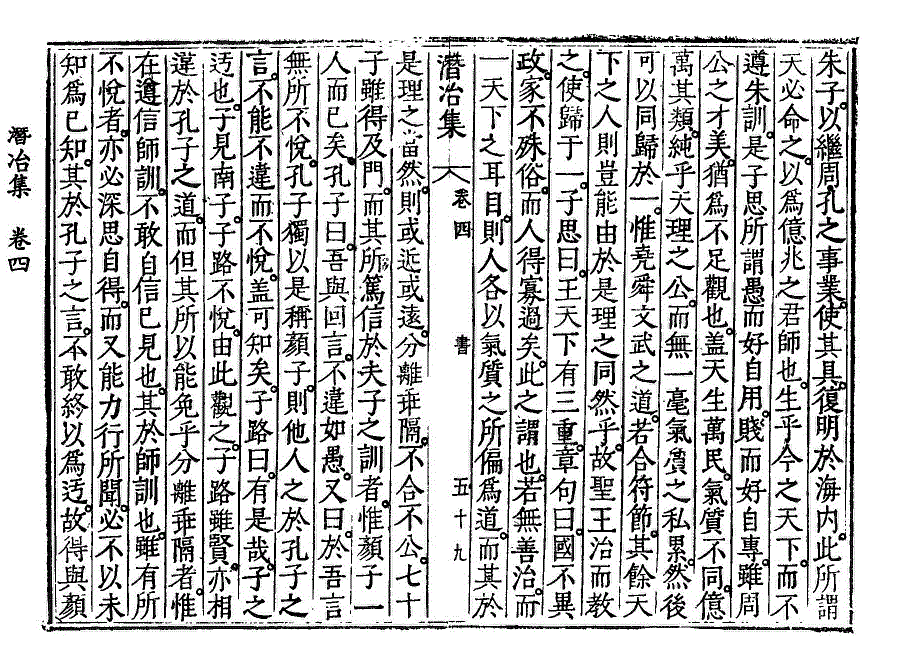 朱子。以继周,孔之事业。使其具。复明于海内。此所谓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也。生乎今之天下。而不遵朱训。是子思所谓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虽周公之才美。犹为不足观也。盖天生万民。气质不同。亿万其类。纯乎天理之公。而无一毫气质之私累。然后可以同归于一。惟尧舜文武之道。若合符节。其馀天下之人则岂能由于是理之同然乎。故圣王治而教之。使归于一。子思曰。王天下有三重。章句曰。国不异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过矣。此之谓也。若无善治。而一天下之耳目。则人各以气质之所偏为道。而其于是理之当然。则或近或远。分离乖隔。不合不公。七十子虽得及门。而其所笃信于夫子之训者。惟颜子一人而已矣。孔子曰。吾与回言。不违如愚。又曰。于吾言无所不悦。孔子独以是称颜子。则他人之于孔子之言。不能不违而不悦。盖可知矣。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子见南子。子路不悦。由此观之。子路虽贤。亦相违于孔子之道。而但其所以能免乎分离乖隔者。惟在遵信师训。不敢自信己见也。其于师训也。虽有所不悦者。亦必深思自得。而又能力行所闻。必不以未知为已知。其于孔子之言。不敢终以为迂。故得与颜
朱子。以继周,孔之事业。使其具。复明于海内。此所谓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也。生乎今之天下。而不遵朱训。是子思所谓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虽周公之才美。犹为不足观也。盖天生万民。气质不同。亿万其类。纯乎天理之公。而无一毫气质之私累。然后可以同归于一。惟尧舜文武之道。若合符节。其馀天下之人则岂能由于是理之同然乎。故圣王治而教之。使归于一。子思曰。王天下有三重。章句曰。国不异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过矣。此之谓也。若无善治。而一天下之耳目。则人各以气质之所偏为道。而其于是理之当然。则或近或远。分离乖隔。不合不公。七十子虽得及门。而其所笃信于夫子之训者。惟颜子一人而已矣。孔子曰。吾与回言。不违如愚。又曰。于吾言无所不悦。孔子独以是称颜子。则他人之于孔子之言。不能不违而不悦。盖可知矣。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子见南子。子路不悦。由此观之。子路虽贤。亦相违于孔子之道。而但其所以能免乎分离乖隔者。惟在遵信师训。不敢自信己见也。其于师训也。虽有所不悦者。亦必深思自得。而又能力行所闻。必不以未知为已知。其于孔子之言。不敢终以为迂。故得与颜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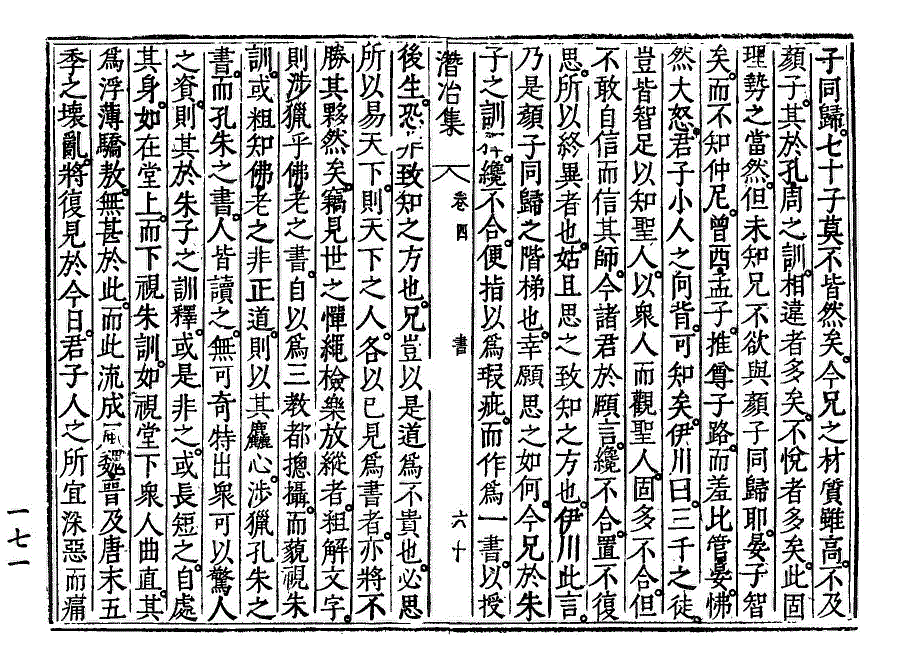 子同归。七十子莫不皆然矣。今兄之材质虽高。不及颜子。其于孔,周之训。相违者多矣。不悦者多矣。此固理势之当然。但未知兄不欲与颜子同归耶。晏子智矣。而不知仲尼。曾西,孟子。推尊子路。而羞比管,晏。怫然大怒。君子小人之向背。可知矣。伊川曰。三千之徒。岂皆智足以知圣人。以众人而观圣人。固多不合。但不敢自信而信其师。今诸君于颐言。才不合。置不复思。所以终异者也。姑且思之致知之方也。伊川此言。乃是颜子同归之阶梯也。幸愿思之如何。今兄于朱子之训释。才不合。便指以为瑕疵。而作为一书。以授后生。恐非致知之方也。兄岂以是道为不贵也。必思所以易天下。则天下之人。各以己见为书者。亦将不胜其夥然矣。窃见世之惮绳检乐放纵者。粗解文字。则涉猎乎佛,老之书。自以为三教都总摄。而藐视朱训。或粗知佛,老之非正道。则以其粗心。涉猎孔朱之书。而孔朱之书。人皆读之。无可奇特出众可以惊人之资。则其于朱子之训释。或是非之。或长短之。自处其身。如在堂上。而下视朱训。如视堂下众人曲直。其为浮薄骄敖。无甚于此。而此流成风魏,晋及唐末五季之坏乱。将复见于今日。君子人之所宜深恶而痛
子同归。七十子莫不皆然矣。今兄之材质虽高。不及颜子。其于孔,周之训。相违者多矣。不悦者多矣。此固理势之当然。但未知兄不欲与颜子同归耶。晏子智矣。而不知仲尼。曾西,孟子。推尊子路。而羞比管,晏。怫然大怒。君子小人之向背。可知矣。伊川曰。三千之徒。岂皆智足以知圣人。以众人而观圣人。固多不合。但不敢自信而信其师。今诸君于颐言。才不合。置不复思。所以终异者也。姑且思之致知之方也。伊川此言。乃是颜子同归之阶梯也。幸愿思之如何。今兄于朱子之训释。才不合。便指以为瑕疵。而作为一书。以授后生。恐非致知之方也。兄岂以是道为不贵也。必思所以易天下。则天下之人。各以己见为书者。亦将不胜其夥然矣。窃见世之惮绳检乐放纵者。粗解文字。则涉猎乎佛,老之书。自以为三教都总摄。而藐视朱训。或粗知佛,老之非正道。则以其粗心。涉猎孔朱之书。而孔朱之书。人皆读之。无可奇特出众可以惊人之资。则其于朱子之训释。或是非之。或长短之。自处其身。如在堂上。而下视朱训。如视堂下众人曲直。其为浮薄骄敖。无甚于此。而此流成风魏,晋及唐末五季之坏乱。将复见于今日。君子人之所宜深恶而痛潜冶先生集卷之四 第 1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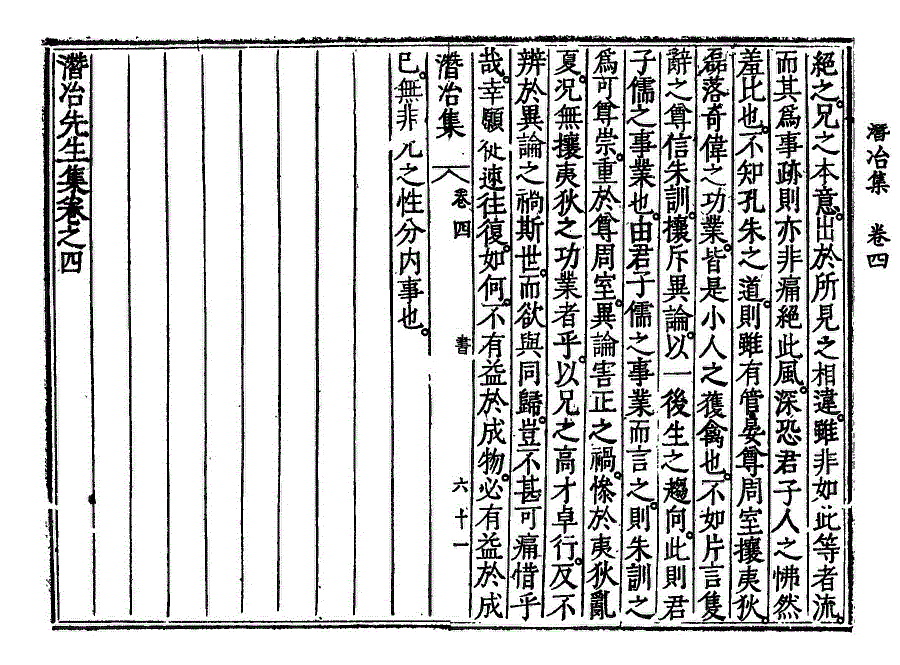 绝之。兄之本意。出于所见之相违。虽非如此等者流。而其为事迹则亦非痛绝此风。深恐君子人之怫然羞比也。不知孔朱之道。则虽有管,晏尊周室攘夷狄。磊落奇伟之功业。皆是小人之获禽也。不如片言只辞之尊信朱训。攘斥异论。以一后生之趋向。此则君子儒之事业也。由君子儒之事业而言之。则朱训之为可尊崇。重于尊周室。异论害正之祸。惨于夷狄乱夏。况无攘夷狄之功业者乎。以兄之高才卓行。反不辨于异论之祸斯世。而欲与同归。岂不甚可痛惜乎哉。幸愿从速往复。如何。不有益于成物。必有益于成已。无非兄之性分内事也。
绝之。兄之本意。出于所见之相违。虽非如此等者流。而其为事迹则亦非痛绝此风。深恐君子人之怫然羞比也。不知孔朱之道。则虽有管,晏尊周室攘夷狄。磊落奇伟之功业。皆是小人之获禽也。不如片言只辞之尊信朱训。攘斥异论。以一后生之趋向。此则君子儒之事业也。由君子儒之事业而言之。则朱训之为可尊崇。重于尊周室。异论害正之祸。惨于夷狄乱夏。况无攘夷狄之功业者乎。以兄之高才卓行。反不辨于异论之祸斯世。而欲与同归。岂不甚可痛惜乎哉。幸愿从速往复。如何。不有益于成物。必有益于成已。无非兄之性分内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