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x 页
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记
记
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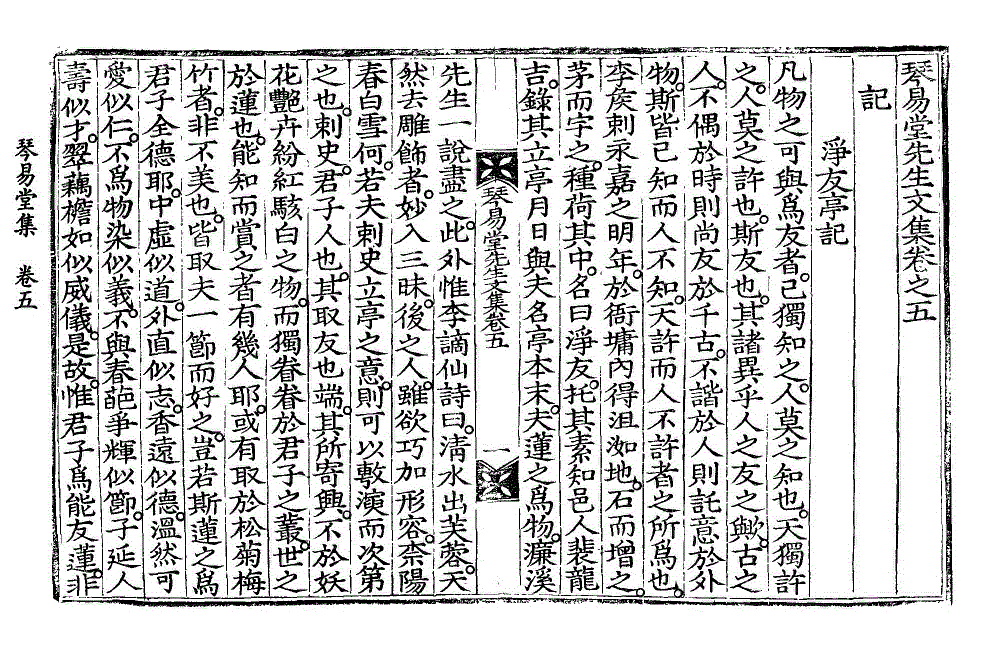 净友亭记
净友亭记凡物之可与为友者。己独知之。人莫之知也。天独许之。人莫之许也。斯友也。其诸异乎人之友之欤。古之人。不偶于时则尚友于千古。不谐于人则托意于外物。斯皆己知而人不知。天许而人不许者之所为也。李侯刺永嘉之明年。于衙墉内得沮洳地。石而增之。茅而宇之。种荷其中。名曰净友。托其素知邑人裴龙吉。录其立亭月日与夫名亭本末。夫莲之为物。濂溪先生一说尽之。此外惟李谪仙诗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者。妙入三昧。后之人。虽欲巧加形容。奈阳春白雪何。若夫刺史立亭之意。则可以敷演而次第之也。刺史。君子人也。其取友也端。其所寄兴。不于妖花艳卉纷红骇白之物。而独眷眷于君子之丛。世之于莲也。能知而赏之者有几人耶。或有取于松菊梅竹者。非不美也。皆取夫一节而好之。岂若斯莲之为君子全德耶。中虚似道。外直似志。香远似德。温然可爱似仁。不为物染似义。不与春葩争辉似节。子延人寿似才。翠藕襜如似威仪。是故。惟君子为能友莲。非
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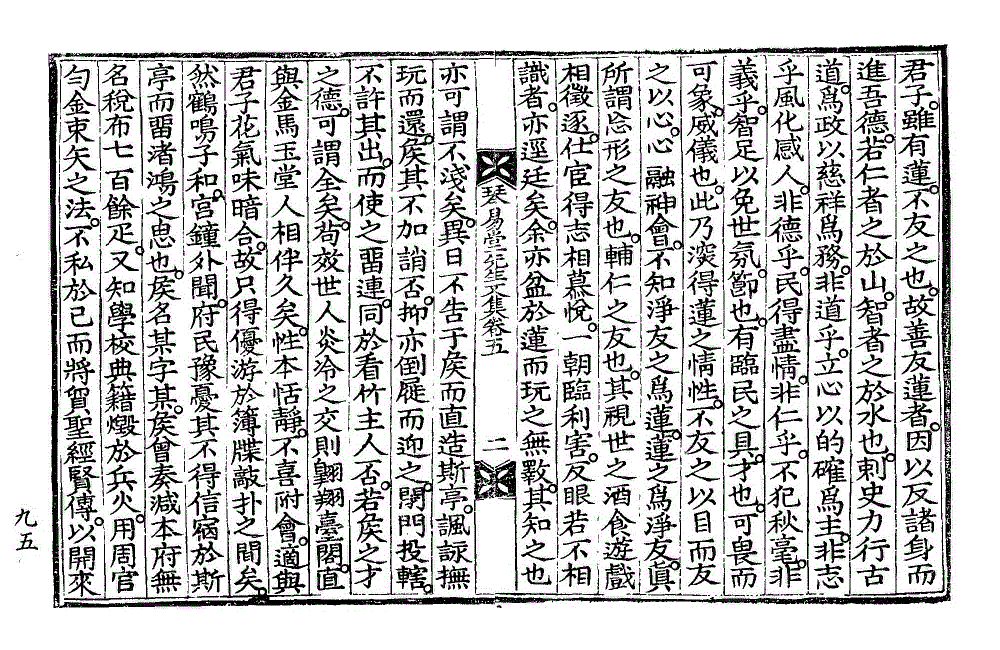 君子。虽有莲。不友之也。故善友莲者。因以反诸身而进吾德。若仁者之于山。智者之于水也。刺史力行古道。为政以慈祥为务。非道乎。立心以的确为主。非志乎风化感人。非德乎。民得尽情。非仁乎。不犯秋毫。非义乎。智足以免世氛。节也。有临民之具。才也。可畏而可象。威仪也。此乃深得莲之情性。不友之以目而友之以心。心融神会。不知净友之为莲。莲之为净友。真所谓忘形之友也。辅仁之友也。其视世之酒食游戏相徵逐。仕宦得志相慕悦。一朝临利害。反眼若不相识者。亦径廷矣。余亦盆于莲而玩之无斁。其知之也亦可谓不浅矣。异日不告于侯而直造斯亭。讽咏抚玩而还。侯其不加诮否。抑亦倒屣而迎之。闭门投辖。不许其出。而使之留连。同于看竹主人否。若侯之才之德。可谓全矣。苟效世人炎冷之交则翱翔台阁。直与金马玉堂人相伴久矣。性本恬静。不喜附会。适与君子花气味暗合。故只得优游于簿牒敲扑之间矣。然鹤鸣子和。宫钟外闻。府民豫忧其不得信宿于斯亭而留渚鸿之思也。侯名某字某。侯曾奏减本府无名税布七百馀疋。又知学校典籍燬于兵火。用周官匀金束矢之法。不私于己而将贸圣经贤传。以开来
君子。虽有莲。不友之也。故善友莲者。因以反诸身而进吾德。若仁者之于山。智者之于水也。刺史力行古道。为政以慈祥为务。非道乎。立心以的确为主。非志乎风化感人。非德乎。民得尽情。非仁乎。不犯秋毫。非义乎。智足以免世氛。节也。有临民之具。才也。可畏而可象。威仪也。此乃深得莲之情性。不友之以目而友之以心。心融神会。不知净友之为莲。莲之为净友。真所谓忘形之友也。辅仁之友也。其视世之酒食游戏相徵逐。仕宦得志相慕悦。一朝临利害。反眼若不相识者。亦径廷矣。余亦盆于莲而玩之无斁。其知之也亦可谓不浅矣。异日不告于侯而直造斯亭。讽咏抚玩而还。侯其不加诮否。抑亦倒屣而迎之。闭门投辖。不许其出。而使之留连。同于看竹主人否。若侯之才之德。可谓全矣。苟效世人炎冷之交则翱翔台阁。直与金马玉堂人相伴久矣。性本恬静。不喜附会。适与君子花气味暗合。故只得优游于簿牒敲扑之间矣。然鹤鸣子和。宫钟外闻。府民豫忧其不得信宿于斯亭而留渚鸿之思也。侯名某字某。侯曾奏减本府无名税布七百馀疋。又知学校典籍燬于兵火。用周官匀金束矢之法。不私于己而将贸圣经贤传。以开来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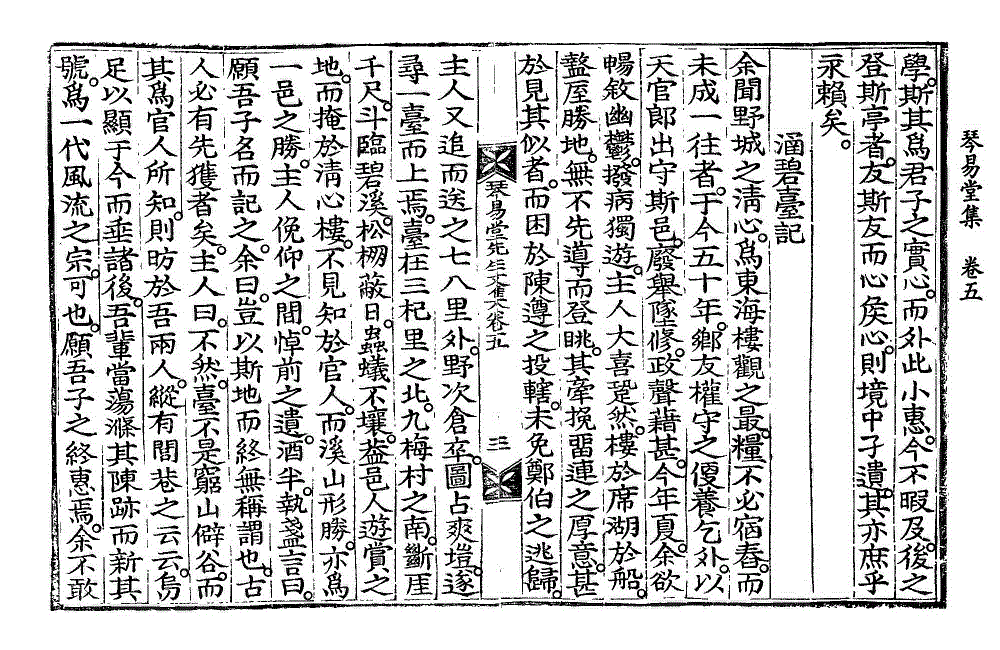 学。斯其为君子之实心。而外此小惠。今不暇及。后之登斯亭者。友斯友而心侯心。则境中孑遗。其亦庶乎永赖矣。
学。斯其为君子之实心。而外此小惠。今不暇及。后之登斯亭者。友斯友而心侯心。则境中孑遗。其亦庶乎永赖矣。涵碧台记
余闻野城之清心。为东海楼观之最。粮不必宿舂。而未成一往者。于今五十年。乡友权守之便养乞外。以天官郎出守斯邑。废举坠修。政声藉甚。今年夏。余欲畅叙幽郁。拨病独游。主人大喜跫然。楼于席湖于船。盩厔胜地。无不先导而登眺。其牵挽留连之厚意。甚于见其似者。而困于陈遵之投辖。未免郑伯之逃归。主人又追而送之七八里外。野次仓卒。图占爽垲。遂寻一台而上焉。台在三杞里之北。九梅村之南。断厓千尺。斗临碧溪。松棚蔽日。虫蚁不壤。盖邑人游赏之地。而掩于清心楼。不见知于官人。而溪山形胜。亦为一邑之胜。主人俛仰之间。悼前之遗。酒半。执盏言曰。愿吾子名而记之。余曰。岂以斯地而终无称谓也。古人必有先获者矣。主人曰。不然。台不是穷山僻谷。而其为官人所知。则昉于吾两人。纵有闾巷之云云。乌足以显于今而垂诸后。吾辈当荡涤其陈迹而新其号。为一代风流之宗。可也。愿吾子之终惠焉。余不敢
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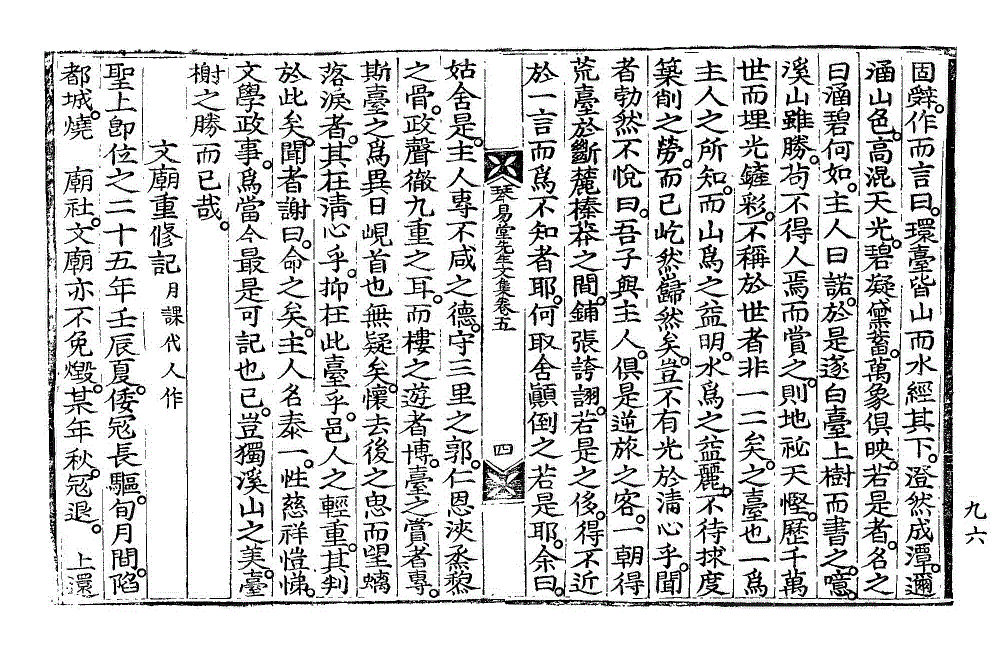 固辞。作而言曰。环台皆山而水经其下。澄然成潭。迩涵山色。高混天光。碧凝黛蓄。万象俱映。若是者。名之曰涵碧何如。主人曰诺。于是遂白台上树而书之。噫。溪山虽胜。苟不得人焉而赏之。则地秘天悭。历千万世而埋光铲彩。不称于世者非一二矣。之台也一为主人之所知。而山为之益明。水为之益丽。不待救度筑削之劳。而已屹然岿然矣。岂不有光于清心乎。闻者勃然不悦曰。吾子与主人。俱是逆旅之客。一朝得荒台于断麓榛莽之间。铺张誇诩。若是之侈。得不近于一言而为不知者耶。何取舍颠倒之若是耶。余曰。姑舍是。主人专不咸之德。守三里之郭。仁恩浃烝黎之骨。政声彻九重之耳。而楼之游者博。台之赏者专。斯台之为异日岘首也无疑矣。怀去后之思而望螭落泪者。其在清心乎。抑在此台乎。邑人之轻重。其判于此矣。闻者谢曰。命之矣。主人名泰一。性慈祥恺悌。文学政事。为当今最是可记也已。岂独溪山之美。台榭之胜而已哉。
固辞。作而言曰。环台皆山而水经其下。澄然成潭。迩涵山色。高混天光。碧凝黛蓄。万象俱映。若是者。名之曰涵碧何如。主人曰诺。于是遂白台上树而书之。噫。溪山虽胜。苟不得人焉而赏之。则地秘天悭。历千万世而埋光铲彩。不称于世者非一二矣。之台也一为主人之所知。而山为之益明。水为之益丽。不待救度筑削之劳。而已屹然岿然矣。岂不有光于清心乎。闻者勃然不悦曰。吾子与主人。俱是逆旅之客。一朝得荒台于断麓榛莽之间。铺张誇诩。若是之侈。得不近于一言而为不知者耶。何取舍颠倒之若是耶。余曰。姑舍是。主人专不咸之德。守三里之郭。仁恩浃烝黎之骨。政声彻九重之耳。而楼之游者博。台之赏者专。斯台之为异日岘首也无疑矣。怀去后之思而望螭落泪者。其在清心乎。抑在此台乎。邑人之轻重。其判于此矣。闻者谢曰。命之矣。主人名泰一。性慈祥恺悌。文学政事。为当今最是可记也已。岂独溪山之美。台榭之胜而已哉。文庙重修记(月课代人作)
圣上即位之二十五年壬辰夏。倭寇长驱。旬月间。陷都城。烧 庙社。文庙亦不免燬。某年秋。寇退。 上还
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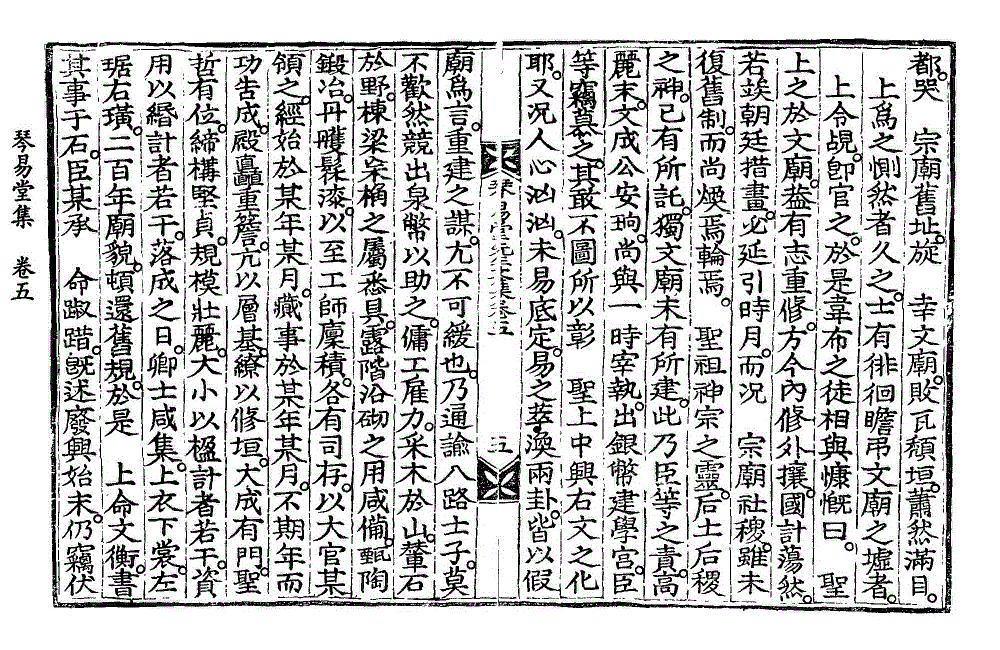 都。哭 宗庙旧址。旋 幸文庙。败瓦颓垣。萧然满目。 上为之恻然者久之。士有徘徊瞻吊文庙之墟者。 上令觇。即官之。于是韦布之徒相与慷慨曰。 圣上之于文庙。盖有志重修。方今内修外攘。国计荡然。若俟朝廷措画。必延引时月。而况 宗庙社稷。虽未复旧制。而尚焕焉轮焉。 圣祖神宗之灵。后土后稷之神。已有所托。独文庙未有所建。此乃臣等之责。高丽末。文成公安珦。尚与一时宰执。出银币建学宫。臣等窃慕之。其敢不图所以彰 圣上中兴右文之化耶。又况人心汹汹。未易底定。易之萃,涣两卦。皆以假庙为言。重建之谋。尤不可缓也。乃通谕八路士子。莫不欢然竞出泉币以助之。佣工雇力。采木于山。辇石于野。栋梁杗桷之属悉具。露阶沿砌之用咸备。甄陶锻冶。丹艧髹漆。以至工师廪积。各有司存。以大官某领之。经始于某年某月。藏事于某年某月。不期年而功告成。殿矗重檐。亢以层基。缭以修垣。大成有门。圣哲有位。缔构坚贞。规模壮丽。大小以楹计者若干。资用以缗计者若干。落成之日。卿士咸集。上衣下裳。左琚右璜。二百年庙貌。顿还旧规。于是 上命文衡。书其事于石。臣某承 命踧踖。既述废兴始末。仍窃伏
都。哭 宗庙旧址。旋 幸文庙。败瓦颓垣。萧然满目。 上为之恻然者久之。士有徘徊瞻吊文庙之墟者。 上令觇。即官之。于是韦布之徒相与慷慨曰。 圣上之于文庙。盖有志重修。方今内修外攘。国计荡然。若俟朝廷措画。必延引时月。而况 宗庙社稷。虽未复旧制。而尚焕焉轮焉。 圣祖神宗之灵。后土后稷之神。已有所托。独文庙未有所建。此乃臣等之责。高丽末。文成公安珦。尚与一时宰执。出银币建学宫。臣等窃慕之。其敢不图所以彰 圣上中兴右文之化耶。又况人心汹汹。未易底定。易之萃,涣两卦。皆以假庙为言。重建之谋。尤不可缓也。乃通谕八路士子。莫不欢然竞出泉币以助之。佣工雇力。采木于山。辇石于野。栋梁杗桷之属悉具。露阶沿砌之用咸备。甄陶锻冶。丹艧髹漆。以至工师廪积。各有司存。以大官某领之。经始于某年某月。藏事于某年某月。不期年而功告成。殿矗重檐。亢以层基。缭以修垣。大成有门。圣哲有位。缔构坚贞。规模壮丽。大小以楹计者若干。资用以缗计者若干。落成之日。卿士咸集。上衣下裳。左琚右璜。二百年庙貌。顿还旧规。于是 上命文衡。书其事于石。臣某承 命踧踖。既述废兴始末。仍窃伏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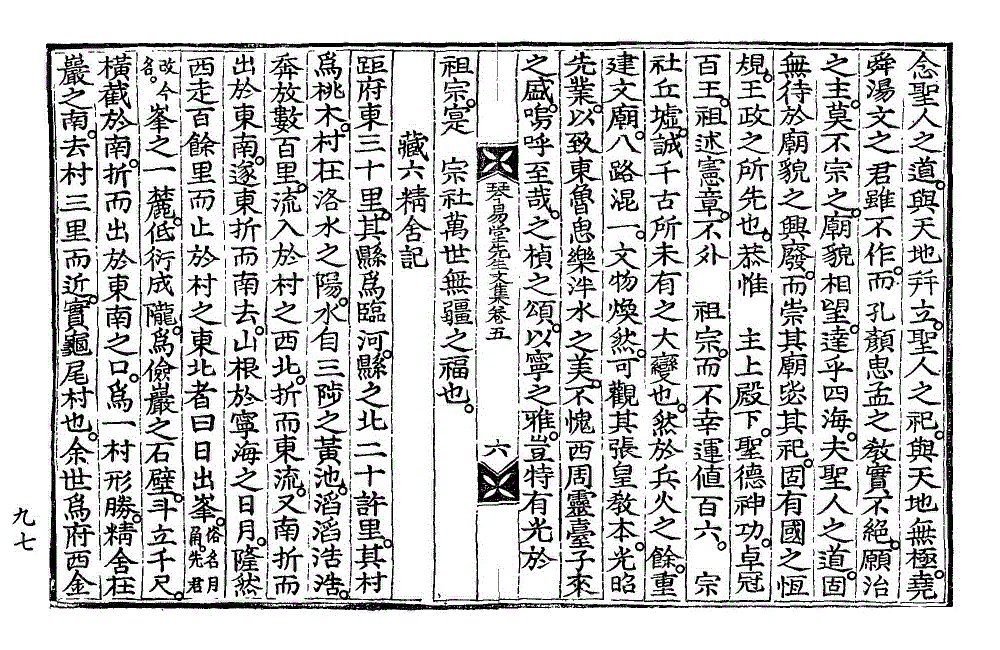 念圣人之道。与天地并立。圣人之祀。与天地无极。尧舜汤文之君虽不作。而孔颜思孟之教实不绝。愿治之主。莫不宗之。庙貌相望。达乎四海。夫圣人之道。固无待于庙貌之兴废。而崇其庙毖其祀。固有国之恒规。王政之所先也。恭惟 主上殿下。圣德神功。卓冠百王。祖述宪章。不外 祖宗。而不幸运值百六。 宗社丘墟。诚千古所未有之大变也。然于兵火之馀。重建文庙。八路混一。文物焕然。可观其张皇教本。光昭先业。以致东鲁思乐泮水之美。不愧西周灵台子来之盛。呜呼至哉。之桢之颂。以宁之雅。岂特有光于 祖宗。寔 宗社万世无疆之福也。
念圣人之道。与天地并立。圣人之祀。与天地无极。尧舜汤文之君虽不作。而孔颜思孟之教实不绝。愿治之主。莫不宗之。庙貌相望。达乎四海。夫圣人之道。固无待于庙貌之兴废。而崇其庙毖其祀。固有国之恒规。王政之所先也。恭惟 主上殿下。圣德神功。卓冠百王。祖述宪章。不外 祖宗。而不幸运值百六。 宗社丘墟。诚千古所未有之大变也。然于兵火之馀。重建文庙。八路混一。文物焕然。可观其张皇教本。光昭先业。以致东鲁思乐泮水之美。不愧西周灵台子来之盛。呜呼至哉。之桢之颂。以宁之雅。岂特有光于 祖宗。寔 宗社万世无疆之福也。藏六精舍记
距府东三十里。其县为临河。县之北二十许里。其村为桃木。村在洛水之阳。水自三陟之黄池。滔滔浩浩。奔放数百里。流入于村之西北。折而东流。又南折而出于东南。遂东折而南去。山根于宁海之日月。隆然西走百馀里而止于村之东北者曰日出峰。(俗名月角。先君改今名。)峰之一麓。低衍成陇。为俭岩之石壁。斗立千尺。横截于南。折而出于东南之口。为一村形胜。精舍在岩之南。去村三里而近。实龟尾村也。余世为府西金
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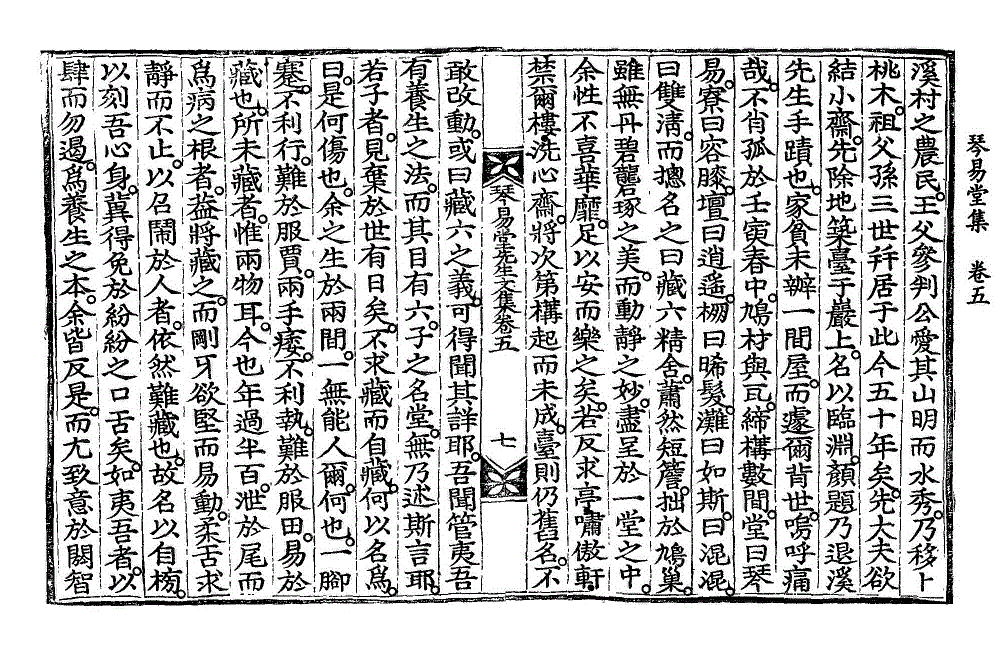 溪村之农民。王父参判公爱其山明而水秀。乃移卜桃木。祖父孙三世并居于此今五十年矣。先大夫欲结小斋。先除地筑台于岩上。名以临渊。颜题乃退溪先生手迹也。家贫未办一间屋。而遽尔背世。呜呼痛哉。不肖孤于壬寅春中。鸠材与瓦。缔构数间。堂曰琴易。寮曰容膝。坛曰逍遥。棚曰晞发。滩曰如斯。曰混混。曰双清。而总名之曰藏六精舍。萧然短檐。拙于鸠巢。虽无丹碧砻琢之美。而动静之妙。尽呈于一堂之中。余性不喜华靡。足以安而乐之矣。若反求亭,啸傲轩禁尔楼,洗心斋。将次第构起而未成。台则仍旧名。不敢改动。或曰藏六之义。可得闻其详耶。吾闻管夷吾有养生之法。而其目有六。子之名堂。无乃述斯言耶。若子者。见弃于世有日矣。不求藏而自藏。何以名为。曰。是何伤也。余之生于两间。一无能人尔。何也。一脚蹇。不利行。难于服贾。两手痿。不利执。难于服田。易于藏也。所未藏者。惟两物耳。今也年过半百。泄于尾而为病之根者。盖将藏之。而刚牙欲坚而易动。柔舌求静而不止。以召闹于人者。依然难藏也。故名以自榜。以刻吾心身。冀得免于纷纷之口舌矣。如夷吾者。以肆而勿遏。为养生之本。余皆反是。而尤致意于阏智
溪村之农民。王父参判公爱其山明而水秀。乃移卜桃木。祖父孙三世并居于此今五十年矣。先大夫欲结小斋。先除地筑台于岩上。名以临渊。颜题乃退溪先生手迹也。家贫未办一间屋。而遽尔背世。呜呼痛哉。不肖孤于壬寅春中。鸠材与瓦。缔构数间。堂曰琴易。寮曰容膝。坛曰逍遥。棚曰晞发。滩曰如斯。曰混混。曰双清。而总名之曰藏六精舍。萧然短檐。拙于鸠巢。虽无丹碧砻琢之美。而动静之妙。尽呈于一堂之中。余性不喜华靡。足以安而乐之矣。若反求亭,啸傲轩禁尔楼,洗心斋。将次第构起而未成。台则仍旧名。不敢改动。或曰藏六之义。可得闻其详耶。吾闻管夷吾有养生之法。而其目有六。子之名堂。无乃述斯言耶。若子者。见弃于世有日矣。不求藏而自藏。何以名为。曰。是何伤也。余之生于两间。一无能人尔。何也。一脚蹇。不利行。难于服贾。两手痿。不利执。难于服田。易于藏也。所未藏者。惟两物耳。今也年过半百。泄于尾而为病之根者。盖将藏之。而刚牙欲坚而易动。柔舌求静而不止。以召闹于人者。依然难藏也。故名以自榜。以刻吾心身。冀得免于纷纷之口舌矣。如夷吾者。以肆而勿遏。为养生之本。余皆反是。而尤致意于阏智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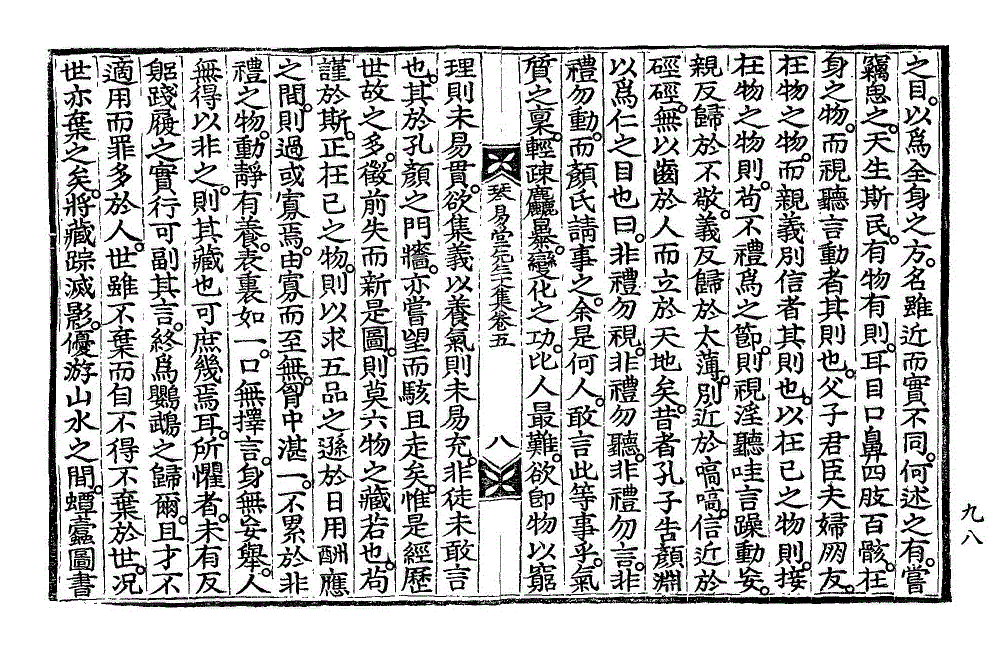 之目。以为全身之方。名虽近而实不同。何述之有。尝窃思之。天生斯民。有物有则。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在身之物。而视听言动者其则也。父子君臣夫妇朋友。在物之物。而亲义别信者其则也。以在己之物则。接在物之物则。苟不礼为之节。则视淫听哇言躁动妄。亲反归于不敬。义反归于太薄。别近于嗃嗃。信近于硁硁。无以齿于人而立于天地矣。昔者孔子告颜渊以为仁之目也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颜氏请事之。余是何人。敢言此等事乎。气质之禀。轻疏粗暴。变化之功。比人最难。欲即物以穷理则未易贯。欲集义以养气则未易充。非徒未敢言也。其于孔颜之门墙。亦尝望而骇且走矣。惟是经历世故之多。徵前失而新是图。则莫六物之藏若也。苟谨于斯。正在己之物。则以求五品之逊于日用酬应之间。则过或寡焉。由寡而至无。胸中湛一。不累于非礼之物。动静有养。表里如一。口无择言。身无妄举。人无得以非之。则其藏也可庶几焉耳。所惧者。未有反躬践履之实行可副其言。终为鹦鹉之归尔。且才不适用而罪多于人。世虽不弃而自不得不弃于世。况世亦弃之矣。将藏踪灭影。优游山水之间。蟫蠹图书
之目。以为全身之方。名虽近而实不同。何述之有。尝窃思之。天生斯民。有物有则。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在身之物。而视听言动者其则也。父子君臣夫妇朋友。在物之物。而亲义别信者其则也。以在己之物则。接在物之物则。苟不礼为之节。则视淫听哇言躁动妄。亲反归于不敬。义反归于太薄。别近于嗃嗃。信近于硁硁。无以齿于人而立于天地矣。昔者孔子告颜渊以为仁之目也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颜氏请事之。余是何人。敢言此等事乎。气质之禀。轻疏粗暴。变化之功。比人最难。欲即物以穷理则未易贯。欲集义以养气则未易充。非徒未敢言也。其于孔颜之门墙。亦尝望而骇且走矣。惟是经历世故之多。徵前失而新是图。则莫六物之藏若也。苟谨于斯。正在己之物。则以求五品之逊于日用酬应之间。则过或寡焉。由寡而至无。胸中湛一。不累于非礼之物。动静有养。表里如一。口无择言。身无妄举。人无得以非之。则其藏也可庶几焉耳。所惧者。未有反躬践履之实行可副其言。终为鹦鹉之归尔。且才不适用而罪多于人。世虽不弃而自不得不弃于世。况世亦弃之矣。将藏踪灭影。优游山水之间。蟫蠹图书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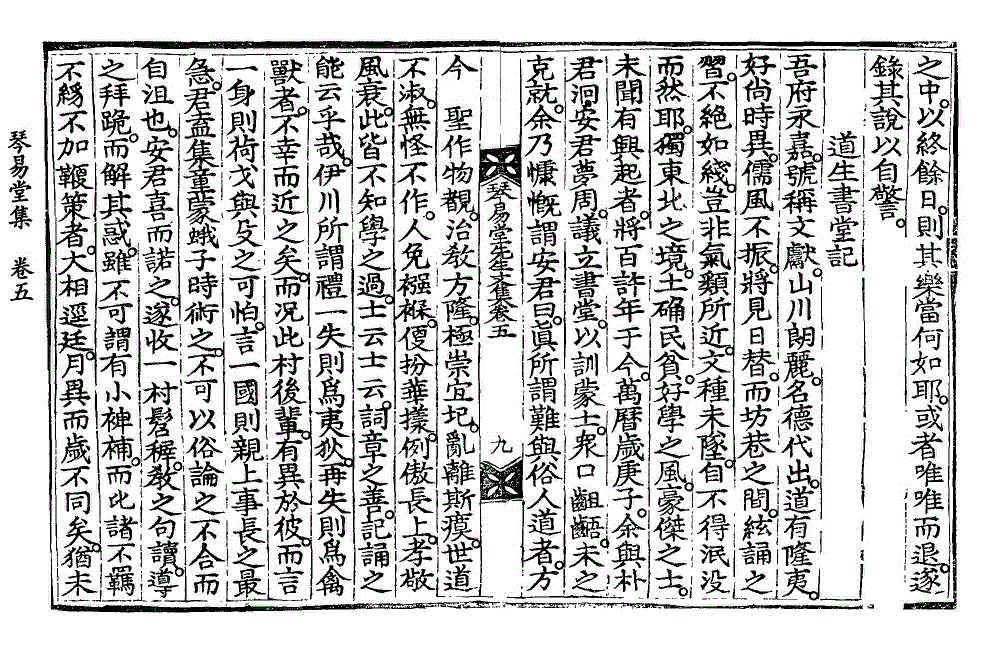 之中。以终馀日。则其乐当何如耶。或者唯唯而退。遂录其说以自警。
之中。以终馀日。则其乐当何如耶。或者唯唯而退。遂录其说以自警。道生书堂记
吾府永嘉。号称文献。山川朗丽。名德代出。道有隆夷。好尚时异。儒风不振。将见日替。而坊巷之间。弦诵之习。不绝如线。岂非气类所近。文种未坠。自不得泯没而然耶。独东北之境。土确民贫。好学之风。豪杰之士。未闻有兴起者。将百许年于今。万历岁庚子。余与朴君泂,安君梦周。议立书堂。以训蒙士。众口龃龉。未之克就。余乃慷慨谓安君曰。真所谓难与俗人道者。方今 圣作物睹。治教方隆。极崇宜圮。乱离斯瘼。世道不淑。无怪不作。人免襁褓。便扮华㨾。例傲长上。孝敬风衰。此皆不知学之过。士云士云。词章之善。记诵之能云乎哉。伊川所谓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者。不幸而近之矣。而况此村后辈。有异于彼。而言一身则荷戈与殳之可怕。言一国则亲上事长之最急。君盍集童蒙蛾子时术之。不可以俗论之不合而自沮也。安君喜而诺之。遂收一村髫稚。教之句读。导之拜跪。而解其惑。虽不可谓有小裨补。而比诸不羁不纼不加鞭策者。大相径廷。月异而岁不同矣。犹未
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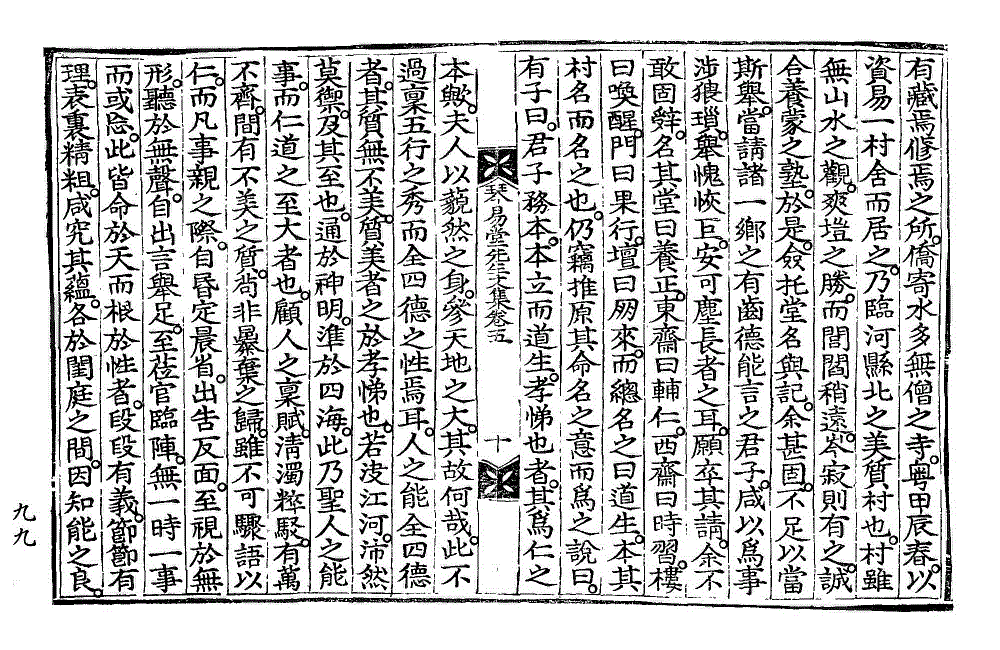 有藏焉修焉之所。侨寄水多无僧之寺。粤甲辰春。以资易一村舍而居之。乃临河县北之美质村也。村虽无山水之观。爽垲之胜。而闾阎稍远。岑寂则有之。诚合养蒙之塾。于是。佥托堂名与记。余甚固。不足以当斯举。当请诸一乡之有齿德能言之君子。咸以为事涉猥琐。举愧恢巨。安可尘长者之耳。愿卒其请。余不敢固辞。名其堂曰养正。东斋曰辅仁。西斋曰时习。楼曰唤醒。门曰果行。坛曰朋来。而总名之曰道生。本其村名而名之也。仍窃推原其命名之意而为之说曰。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夫人以藐然之身。参天地之大。其故何哉。此不过禀五行之秀而全四德之性焉耳。人之能全四德者。其质无不美。质美者之于孝悌也。若决江河。沛然莫御。及其至也。通于神明。准于四海。此乃圣人之能事。而仁道之至大者也。顾人之禀赋。清浊粹驳。有万不齐。间有不美之质。苟非暴弃之归。虽不可骤语以仁。而凡事亲之际。自昏定晨省。出告反面。至视于无形。听于无声。自出言举足。至莅官临阵。无一时一事而或忘。此皆命于天而根于性者。段段有义。节节有理。表里精粗。咸究其蕴。各于闺庭之间。因知能之良。
有藏焉修焉之所。侨寄水多无僧之寺。粤甲辰春。以资易一村舍而居之。乃临河县北之美质村也。村虽无山水之观。爽垲之胜。而闾阎稍远。岑寂则有之。诚合养蒙之塾。于是。佥托堂名与记。余甚固。不足以当斯举。当请诸一乡之有齿德能言之君子。咸以为事涉猥琐。举愧恢巨。安可尘长者之耳。愿卒其请。余不敢固辞。名其堂曰养正。东斋曰辅仁。西斋曰时习。楼曰唤醒。门曰果行。坛曰朋来。而总名之曰道生。本其村名而名之也。仍窃推原其命名之意而为之说曰。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夫人以藐然之身。参天地之大。其故何哉。此不过禀五行之秀而全四德之性焉耳。人之能全四德者。其质无不美。质美者之于孝悌也。若决江河。沛然莫御。及其至也。通于神明。准于四海。此乃圣人之能事。而仁道之至大者也。顾人之禀赋。清浊粹驳。有万不齐。间有不美之质。苟非暴弃之归。虽不可骤语以仁。而凡事亲之际。自昏定晨省。出告反面。至视于无形。听于无声。自出言举足。至莅官临阵。无一时一事而或忘。此皆命于天而根于性者。段段有义。节节有理。表里精粗。咸究其蕴。各于闺庭之间。因知能之良。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00H 页
 尽善事之方。则日用发见。无非此仁。父母之顺。昆弟之和。可以驯致而同归于美质之人矣。是以。小学始功。专在于爱亲敬兄隆师亲友之间。洒埽应对进退周旋之节。而程子亦以为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又曰。洒埽应对。便可到圣人事。又曰。洒埽应对。便是形而上者。此岂高远难行之事哉。而今日命名之义。所以必主于孝悌者。以其专为童蒙始学者而设也。登斯堂者。亦不可外此而别求幽深之术。只于扁额。顾名思义。习必至于悦。友必辅之仁。昏必唤之醒。而所养者无不正。所行者无不果。有所不知焉则进而问诸师。又有所不通焉则退而质之友。立舜人予人之志。加人百己千之功。则本立而道生。终致朋来之乐。何患乎气质之难变。而圣贤之不可学哉。曾子之一贯本于斯。颜氏之四勿本于斯。人病不为耳。为之则非由外铄我也。只在五身上而已。他日出而立乎人之本朝。由是而忠于君。由是而顺于长。于凡天下之事。直举此而措之耳。孟子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政谓此也。所惧者。科第而诱之。利禄以陷之。惟雕虫篆刻是习。惟风云月露是尚。丧其良心。人欲滔天。所学非所行。所行非所学。其在家也。阋墙紾臂。德色谇语。
尽善事之方。则日用发见。无非此仁。父母之顺。昆弟之和。可以驯致而同归于美质之人矣。是以。小学始功。专在于爱亲敬兄隆师亲友之间。洒埽应对进退周旋之节。而程子亦以为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又曰。洒埽应对。便可到圣人事。又曰。洒埽应对。便是形而上者。此岂高远难行之事哉。而今日命名之义。所以必主于孝悌者。以其专为童蒙始学者而设也。登斯堂者。亦不可外此而别求幽深之术。只于扁额。顾名思义。习必至于悦。友必辅之仁。昏必唤之醒。而所养者无不正。所行者无不果。有所不知焉则进而问诸师。又有所不通焉则退而质之友。立舜人予人之志。加人百己千之功。则本立而道生。终致朋来之乐。何患乎气质之难变。而圣贤之不可学哉。曾子之一贯本于斯。颜氏之四勿本于斯。人病不为耳。为之则非由外铄我也。只在五身上而已。他日出而立乎人之本朝。由是而忠于君。由是而顺于长。于凡天下之事。直举此而措之耳。孟子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政谓此也。所惧者。科第而诱之。利禄以陷之。惟雕虫篆刻是习。惟风云月露是尚。丧其良心。人欲滔天。所学非所行。所行非所学。其在家也。阋墙紾臂。德色谇语。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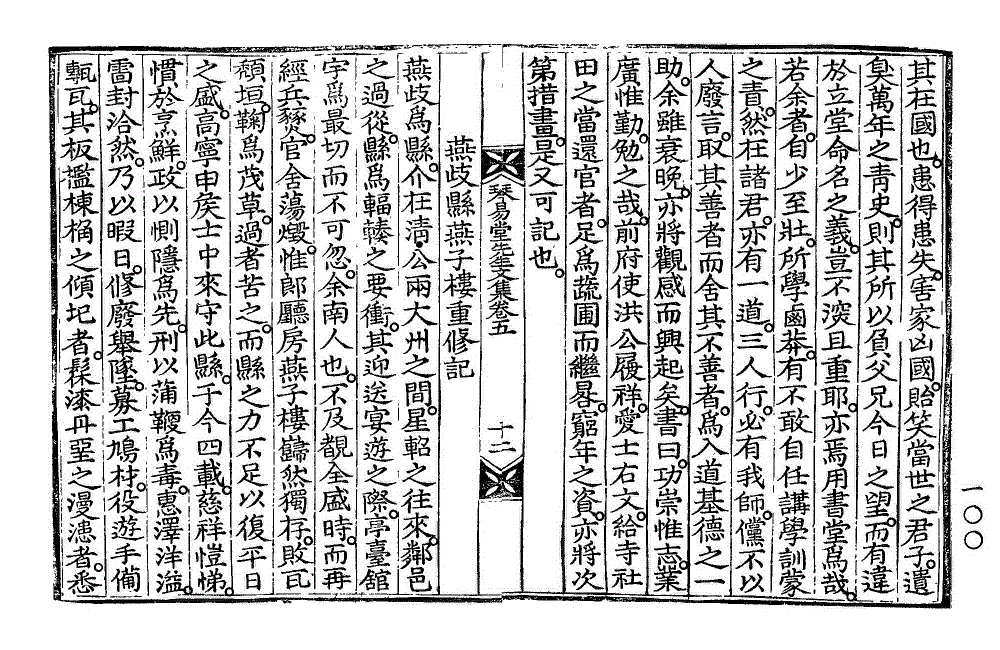 其在国也。患得患失。害家凶国。贻笑当世之君子。遗臭万年之青史。则其所以负父兄今日之望。而有违于立堂命名之义。岂不深且重耶。亦焉用书堂为哉。若余者。自少至壮。所学卤莽。有不敢自任讲学训蒙之责。然在诸君。亦有一道。三人行。必有我师。傥不以人废言。取其善者而舍其不善者。为入道基德之一助。余虽衰晚。亦将观感而兴起矣。书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勉之哉。前府使洪公履祥。爱士右文。给寺社田之当还官者。足为蔬圃而继晷。穷年之资。亦将次第措画。是又可记也。
其在国也。患得患失。害家凶国。贻笑当世之君子。遗臭万年之青史。则其所以负父兄今日之望。而有违于立堂命名之义。岂不深且重耶。亦焉用书堂为哉。若余者。自少至壮。所学卤莽。有不敢自任讲学训蒙之责。然在诸君。亦有一道。三人行。必有我师。傥不以人废言。取其善者而舍其不善者。为入道基德之一助。余虽衰晚。亦将观感而兴起矣。书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勉之哉。前府使洪公履祥。爱士右文。给寺社田之当还官者。足为蔬圃而继晷。穷年之资。亦将次第措画。是又可记也。燕岐县燕子楼重修记
燕岐为县。介在清,公两大州之间。星轺之往来。邻邑之过从。县为辐辏之要冲。其迎送宴游之际。亭台馆宇为最切而不可忽。余南人也。不及睹全盛时。而再经兵燹。官舍荡燬。惟郎厅房燕子楼岿然独存。败瓦颓垣。鞠为茂草。过者苦之。而县之力不足以复平日之盛。高宁申侯士中来守此县。于今四载。慈祥恺悌。惯于烹鲜。政以恻隐为先。刑以蒲鞭为毒。惠泽洋溢。雷封洽然。乃以暇日。修废举坠。募工鸠材。役游手备砖瓦。其板槛栋桷之倾圮者。髹漆丹垩之漫漶者。悉
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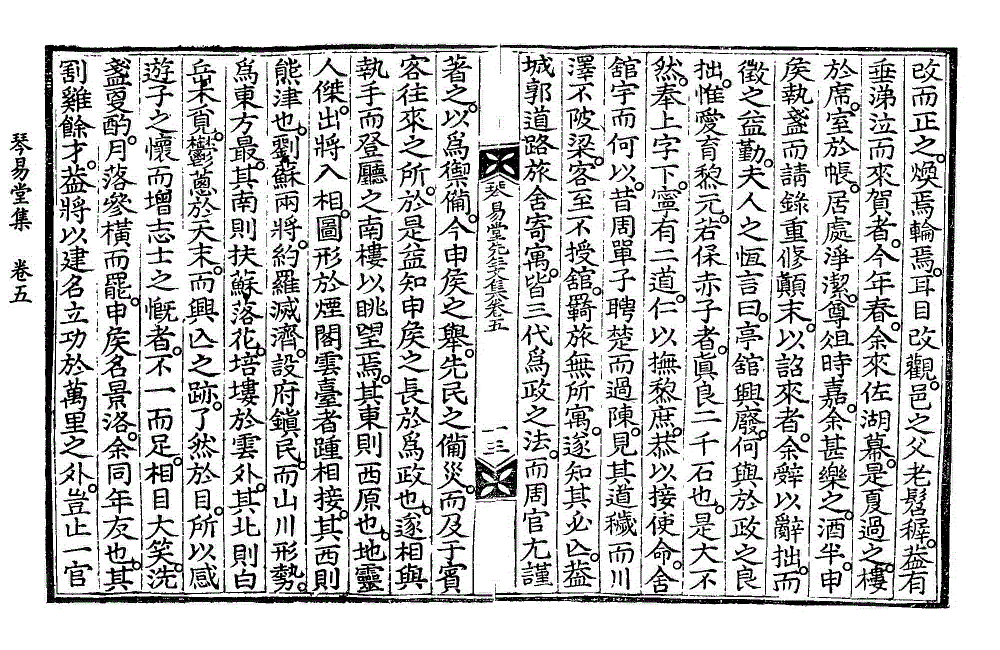 改而正之。焕焉轮焉。耳目改观。邑之父老髫稚。盖有垂涕泣而来贺者。今年春。余来佐湖幕。是夏过之。楼于席。室于帐。居处净洁。尊俎时嘉。余甚乐之。酒半。申侯执盏而请录重修颠末。以诏来者。余辞以辞拙。而徵之益勤。夫人之恒言曰。亭馆兴废。何与于政之良拙。惟爱育黎元。若保赤子者。真良二千石也。是大不然。奉上字下。宁有二道。仁以抚黎庶。恭以接使命。舍馆宇而何以。昔周单子聘楚而过陈。见其道秽而川泽不陂梁。客至不授馆。羁旅无所寓。遂知其必亡。盖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为政之法。而周官尤谨著之。以为御备。今申侯之举。先民之备灾。而及于宾客往来之所。于是益知申侯之长于为政也。遂相与执手而登厅之南楼以眺望焉。其东则西原也。地灵人杰。出将入相。图形于烟阁云台者踵相接。其西则熊津也。刘,苏两将。约罗灭济。设府镇民。而山川形势。为东方最。其南则扶苏,落花。培塿于云外。其北则白岳,木觅。郁葱于天末。而兴亡之迹。了然于目。所以感游子之怀而增志士之慨者。不一而足。相目大笑。洗盏更酌。月落参横而罢。申侯名景洛。余同年友也。其割鸡馀才。盖将以建名立功于万里之外。岂止一官
改而正之。焕焉轮焉。耳目改观。邑之父老髫稚。盖有垂涕泣而来贺者。今年春。余来佐湖幕。是夏过之。楼于席。室于帐。居处净洁。尊俎时嘉。余甚乐之。酒半。申侯执盏而请录重修颠末。以诏来者。余辞以辞拙。而徵之益勤。夫人之恒言曰。亭馆兴废。何与于政之良拙。惟爱育黎元。若保赤子者。真良二千石也。是大不然。奉上字下。宁有二道。仁以抚黎庶。恭以接使命。舍馆宇而何以。昔周单子聘楚而过陈。见其道秽而川泽不陂梁。客至不授馆。羁旅无所寓。遂知其必亡。盖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为政之法。而周官尤谨著之。以为御备。今申侯之举。先民之备灾。而及于宾客往来之所。于是益知申侯之长于为政也。遂相与执手而登厅之南楼以眺望焉。其东则西原也。地灵人杰。出将入相。图形于烟阁云台者踵相接。其西则熊津也。刘,苏两将。约罗灭济。设府镇民。而山川形势。为东方最。其南则扶苏,落花。培塿于云外。其北则白岳,木觅。郁葱于天末。而兴亡之迹。了然于目。所以感游子之怀而增志士之慨者。不一而足。相目大笑。洗盏更酌。月落参横而罢。申侯名景洛。余同年友也。其割鸡馀才。盖将以建名立功于万里之外。岂止一官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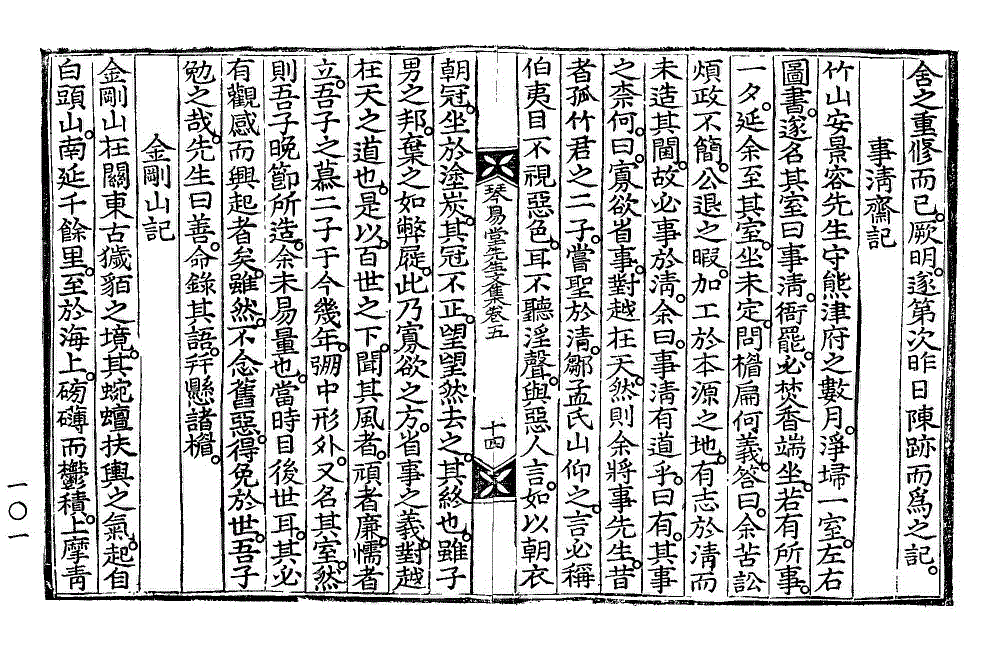 舍之重修而已。厥明。遂第次昨日陈迹而为之记。
舍之重修而已。厥明。遂第次昨日陈迹而为之记。事清斋记
竹山安景容先生守熊津府之数月。净埽一室。左右图书。遂名其室曰事清。衙罢。必焚香端坐。若有所事。一夕。延余至其室。坐未定。问楣扁何义。答曰。余苦讼烦政不简。公退之暇。加工于本源之地。有志于清而未造其阃。故必事于清。余曰。事清有道乎。曰有。其事之奈何。曰。寡欲省事。对越在天。然则余将事先生。昔者孤竹君之二子。尝圣于清。邹孟氏山仰之。言必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其终也。虽子男之邦。弃之如弊屣。此乃寡欲之方。省事之义。对越在天之道也。是以。百世之下。闻其风者。顽者廉。懦者立。吾子之慕二子于今几年。弸中形外。又名其室。然则吾子晚节所造。余未易量也。当时目后世耳。其必有观感而兴起者矣。虽然。不念旧恶。得免于世。吾子勉之哉。先生曰善。命录其语。并悬诸楣。
金刚山记
金刚山在关东古獩貊之境。其蜿蟺扶舆之气。起自白头山。南延千馀里。至于海上。磅礴而郁积。上摩青
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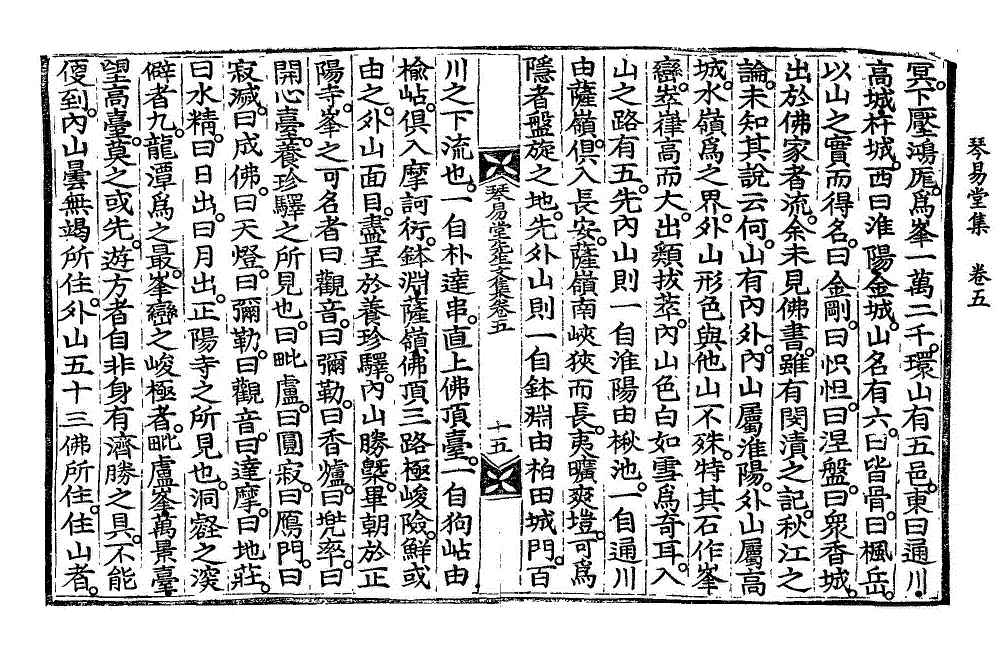 冥。下压鸿厖。为峰一万二千。环山有五邑。东曰通川,高城,杆城。西曰淮阳,金城。山名有六。曰皆骨。曰枫岳。以山之实而得名。曰金刚。曰怾怛。曰涅盘。曰众香城。出于佛家者流。余未见佛书。虽有闵渍之记。秋江之论。未知其说云何。山有内外。内山属淮阳。外山属高城。水岭为之界。外山形色与他山不殊。特其石作峰峦。崒嵂高而大。出类拔萃。内山色白如雪为奇耳。入山之路有五。先内山则一自淮阳由楸池。一自通川由萨岭。俱入长安。萨岭南峡狭而长。夷旷爽垲。可为隐者盘旋之地。先外山则一自钵渊由柏田城门。百川之下流也。一自朴达串。直上佛顶台。一自狗岾由榆岾。俱入摩诃衍。钵渊,萨岭,佛顶三路极峻险。鲜或由之。外山面目。尽呈于养珍驿。内山胜概。毕朝于正阳寺。峰之可名者曰观音。曰弥勒。曰香炉。曰兜率。曰开心台。养珍驿之所见也。曰毗卢。曰圆寂。曰雁门。曰寂灭。曰成佛。曰天灯。曰弥勒。曰观音。曰达摩。曰地庄。曰水精。曰日出。曰月出。正阳寺之所见也。洞壑之深僻者九。龙潭为之最。峰峦之峻极者。毗卢峰,万景台,望高台。莫之或先。游方者自非身有济胜之具。不能便到。内山昙无竭所住。外山五十三佛所住。住山者。
冥。下压鸿厖。为峰一万二千。环山有五邑。东曰通川,高城,杆城。西曰淮阳,金城。山名有六。曰皆骨。曰枫岳。以山之实而得名。曰金刚。曰怾怛。曰涅盘。曰众香城。出于佛家者流。余未见佛书。虽有闵渍之记。秋江之论。未知其说云何。山有内外。内山属淮阳。外山属高城。水岭为之界。外山形色与他山不殊。特其石作峰峦。崒嵂高而大。出类拔萃。内山色白如雪为奇耳。入山之路有五。先内山则一自淮阳由楸池。一自通川由萨岭。俱入长安。萨岭南峡狭而长。夷旷爽垲。可为隐者盘旋之地。先外山则一自钵渊由柏田城门。百川之下流也。一自朴达串。直上佛顶台。一自狗岾由榆岾。俱入摩诃衍。钵渊,萨岭,佛顶三路极峻险。鲜或由之。外山面目。尽呈于养珍驿。内山胜概。毕朝于正阳寺。峰之可名者曰观音。曰弥勒。曰香炉。曰兜率。曰开心台。养珍驿之所见也。曰毗卢。曰圆寂。曰雁门。曰寂灭。曰成佛。曰天灯。曰弥勒。曰观音。曰达摩。曰地庄。曰水精。曰日出。曰月出。正阳寺之所见也。洞壑之深僻者九。龙潭为之最。峰峦之峻极者。毗卢峰,万景台,望高台。莫之或先。游方者自非身有济胜之具。不能便到。内山昙无竭所住。外山五十三佛所住。住山者。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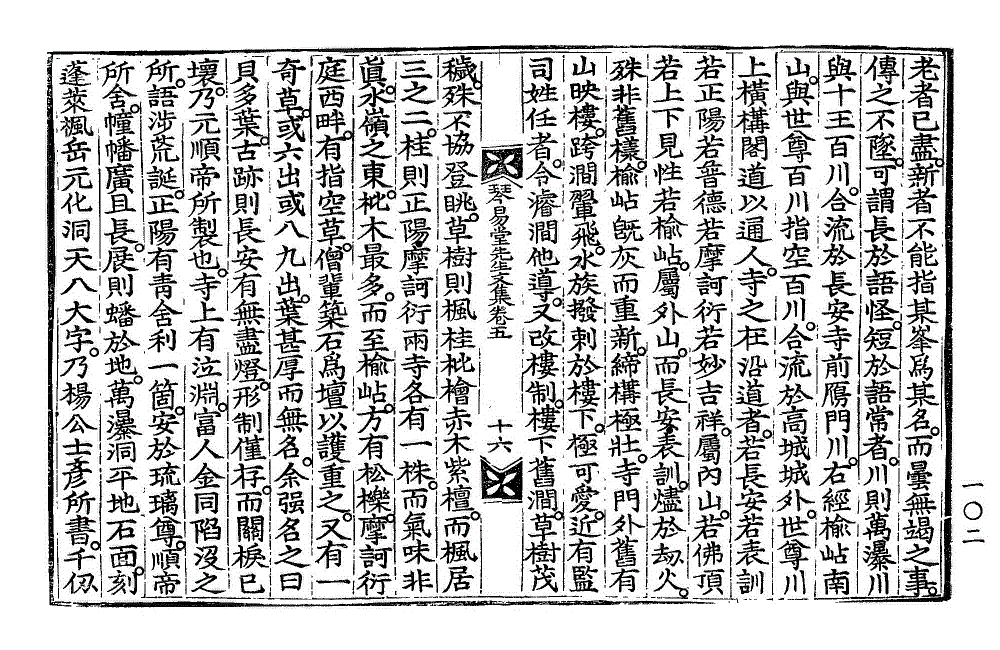 老者已尽。新者不能指某峰为某名。而昙无竭之事。传之不坠。可谓长于语怪。短于语常者。川则万瀑川与十王百川。合流于长安寺前雁门川。右经榆岾南山。与世尊百川指空百川。合流于高城城外。世尊川上横构阁道以通人。寺之在沿道者。若长安若表训若正阳若普德若摩诃衍若妙吉祥。属内山。若佛顶若上下见性若榆岾。属外山。而长安,表训。烬于劫火。殊非旧样。榆岾既灰而重新。缔构极壮。寺门外旧有山映楼。跨涧翚飞。水族拨刺于楼下。极可爱。近有监司姓任者。令浚涧他导。又改楼制。楼下旧涧。草树茂秽。殊不协登眺。草树则枫桂枇桧赤木紫檀。而枫居三之二。桂则正阳,摩诃衍两寺各有一株。而气味非真。水岭之东。枇木最多。而至榆岾。方有松栎。摩诃衍庭西畔。有指空草。僧辈筑石为坛以护重之。又有一奇草。或六出或八九出。叶甚厚而无名。余强名之曰贝多叶。古迹则长安有无尽灯。形制仅存。而关棙已坏。乃元顺帝所制也。寺上有泣渊。富人金同陷没之所。语涉莣诞。正阳有青舍利一个。安于琉璃尊。顺帝所舍。幢幡广且长。展则蟠于地。万瀑洞平地石面。刻蓬莱枫岳元化洞天八大字。乃杨公士彦所书。千仞
老者已尽。新者不能指某峰为某名。而昙无竭之事。传之不坠。可谓长于语怪。短于语常者。川则万瀑川与十王百川。合流于长安寺前雁门川。右经榆岾南山。与世尊百川指空百川。合流于高城城外。世尊川上横构阁道以通人。寺之在沿道者。若长安若表训若正阳若普德若摩诃衍若妙吉祥。属内山。若佛顶若上下见性若榆岾。属外山。而长安,表训。烬于劫火。殊非旧样。榆岾既灰而重新。缔构极壮。寺门外旧有山映楼。跨涧翚飞。水族拨刺于楼下。极可爱。近有监司姓任者。令浚涧他导。又改楼制。楼下旧涧。草树茂秽。殊不协登眺。草树则枫桂枇桧赤木紫檀。而枫居三之二。桂则正阳,摩诃衍两寺各有一株。而气味非真。水岭之东。枇木最多。而至榆岾。方有松栎。摩诃衍庭西畔。有指空草。僧辈筑石为坛以护重之。又有一奇草。或六出或八九出。叶甚厚而无名。余强名之曰贝多叶。古迹则长安有无尽灯。形制仅存。而关棙已坏。乃元顺帝所制也。寺上有泣渊。富人金同陷没之所。语涉莣诞。正阳有青舍利一个。安于琉璃尊。顺帝所舍。幢幡广且长。展则蟠于地。万瀑洞平地石面。刻蓬莱枫岳元化洞天八大字。乃杨公士彦所书。千仞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03H 页
 石角。有鹤巢。青鹤方拗颈。拳一足以眠。普德窟观音殿。一角安于铜柱。一角安于木柱。悬空以构。如燕巢然。复以两铁索。一端钉殿柱。一端钉岩石以缠缚之。下临千尺。人行殿上则动摇可怕。摩诃衍一高峰有穴。可洞望妙吉祥下石壁刻弥勒像。乃延祐二年四月也。榆岾有顺帝所舍臧获敕及本朝 世祖大王舍身旨。末有惠雄惠温惠屹小红篆。山之一枝。东北延于通川郡之海边。为丛石亭。沿陆四五里。石大如柱。皆出六面。长或二三丈或五六丈。或合百馀柱为一丛。或合四五十柱为一丛。或离立海中。或附立陆地。中半以南。竖立作峰。以北横积作堆。其中四峰最高且奇。名曰四仙峰。堆者或如莲房。或如俗制龟文枕头。或如歪脚床脚。而各有条理。海中距陆六七里有岛。穴可通舟。其石断处亦皆六面。如泻蜜蜂房悬在空中。若非方舟入海。不能穷其瑰玮谲诡之观。安边国岛之石亦然。此亭之脉。必根于国岛。土人云。
石角。有鹤巢。青鹤方拗颈。拳一足以眠。普德窟观音殿。一角安于铜柱。一角安于木柱。悬空以构。如燕巢然。复以两铁索。一端钉殿柱。一端钉岩石以缠缚之。下临千尺。人行殿上则动摇可怕。摩诃衍一高峰有穴。可洞望妙吉祥下石壁刻弥勒像。乃延祐二年四月也。榆岾有顺帝所舍臧获敕及本朝 世祖大王舍身旨。末有惠雄惠温惠屹小红篆。山之一枝。东北延于通川郡之海边。为丛石亭。沿陆四五里。石大如柱。皆出六面。长或二三丈或五六丈。或合百馀柱为一丛。或合四五十柱为一丛。或离立海中。或附立陆地。中半以南。竖立作峰。以北横积作堆。其中四峰最高且奇。名曰四仙峰。堆者或如莲房。或如俗制龟文枕头。或如歪脚床脚。而各有条理。海中距陆六七里有岛。穴可通舟。其石断处亦皆六面。如泻蜜蜂房悬在空中。若非方舟入海。不能穷其瑰玮谲诡之观。安边国岛之石亦然。此亭之脉。必根于国岛。土人云。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跋
潜溪求针录跋
余自蚤岁。不喜词藻。非为其不切于心身而然也。性不近也。近得白氏集读之。颇有会心处。始知诗之蹊
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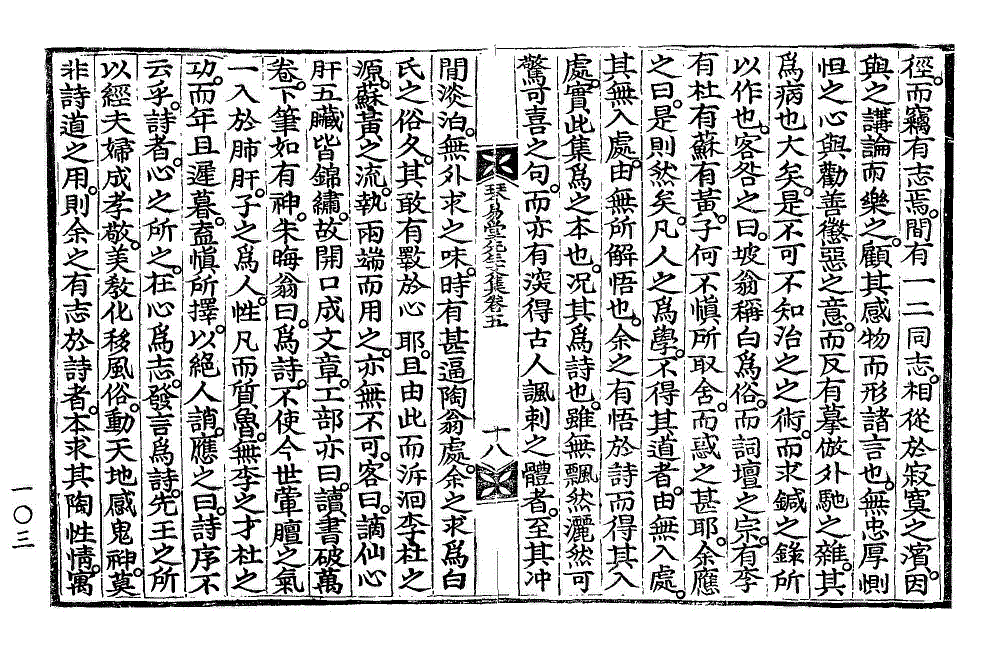 径。而窃有志焉。间有一二同志。相从于寂寞之滨。因与之讲论而乐之。顾其感物而形诸言也。无忠厚恻怛之心与劝善惩恶之意。而反有摹仿外驰之杂。其为病也大矣。是不可不知治之之术。而求针之录所以作也。客咎之曰。坡翁称白为俗。而词坛之宗。有李有杜有苏有黄。子何不慎所取舍。而惑之甚耶。余应之曰。是则然矣。凡人之为学。不得其道者。由无入处。其无入处。由无所解悟也。余之有悟于诗而得其入处。实此集为之本也。况其为诗也。虽无飘然洒然可惊可喜之句。而亦有深得古人讽刺之体者。至其冲閒淡泊。无外求之味。时有甚逼陶翁处。余之求为白氏之俗久。其敢有斁于心耶。且由此而溯洄李,杜之源。苏,黄之流。执两端而用之。亦无不可。客曰。谪仙心肝五脏皆锦绣。故开口成文章。工部亦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朱晦翁曰。为诗。不使今世荤膻之气一入于肺肝。子之为人。性凡而质鲁。无李之才杜之功。而年且迟暮。盍慎所择。以绝人诮。应之曰。诗序不云乎。诗者。心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先王之所以经夫妇成孝敬。美教化移风俗。动天地感鬼神。莫非诗道之用。则余之有志于诗者。本求其陶性情。寓
径。而窃有志焉。间有一二同志。相从于寂寞之滨。因与之讲论而乐之。顾其感物而形诸言也。无忠厚恻怛之心与劝善惩恶之意。而反有摹仿外驰之杂。其为病也大矣。是不可不知治之之术。而求针之录所以作也。客咎之曰。坡翁称白为俗。而词坛之宗。有李有杜有苏有黄。子何不慎所取舍。而惑之甚耶。余应之曰。是则然矣。凡人之为学。不得其道者。由无入处。其无入处。由无所解悟也。余之有悟于诗而得其入处。实此集为之本也。况其为诗也。虽无飘然洒然可惊可喜之句。而亦有深得古人讽刺之体者。至其冲閒淡泊。无外求之味。时有甚逼陶翁处。余之求为白氏之俗久。其敢有斁于心耶。且由此而溯洄李,杜之源。苏,黄之流。执两端而用之。亦无不可。客曰。谪仙心肝五脏皆锦绣。故开口成文章。工部亦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朱晦翁曰。为诗。不使今世荤膻之气一入于肺肝。子之为人。性凡而质鲁。无李之才杜之功。而年且迟暮。盍慎所择。以绝人诮。应之曰。诗序不云乎。诗者。心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先王之所以经夫妇成孝敬。美教化移风俗。动天地感鬼神。莫非诗道之用。则余之有志于诗者。本求其陶性情。寓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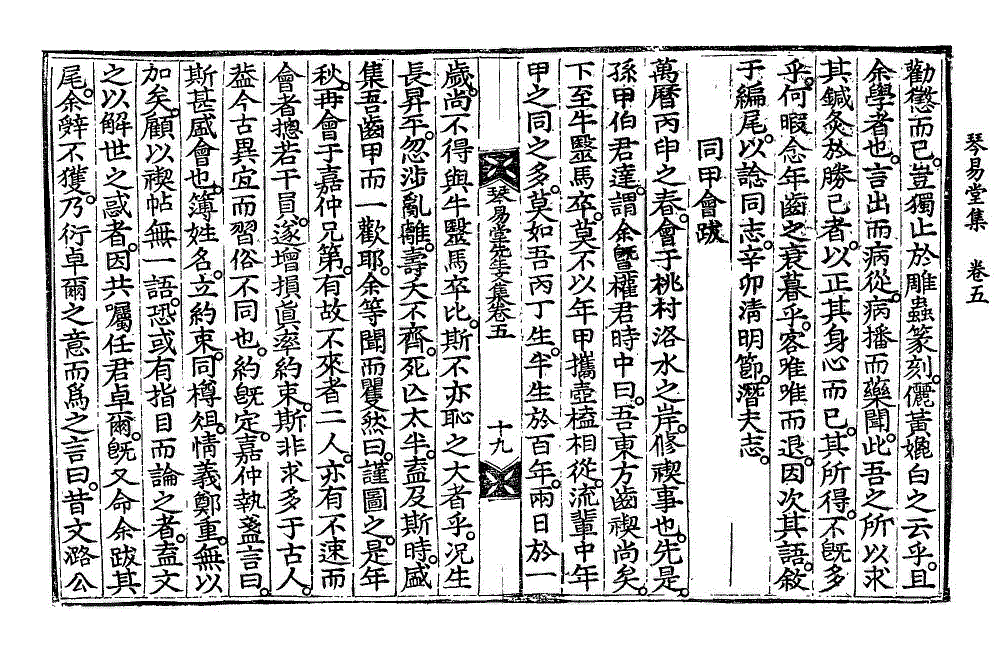 劝惩而已。岂独止于雕虫篆刻。俪黄媲白之云乎。且余学者也。言出而病从。病播而药闻。此吾之所以求其针灸于胜己者。以正其身心而已。其所得。不既多乎。何暇念年齿之衰暮乎。客唯唯而退。因次其语。叙于编尾。以谂同志。辛卯清明节。潜夫志。
劝惩而已。岂独止于雕虫篆刻。俪黄媲白之云乎。且余学者也。言出而病从。病播而药闻。此吾之所以求其针灸于胜己者。以正其身心而已。其所得。不既多乎。何暇念年齿之衰暮乎。客唯唯而退。因次其语。叙于编尾。以谂同志。辛卯清明节。潜夫志。同甲会跋
万历丙申之春。会于桃村洛水之岸。修禊事也。先是。孙甲伯君达。谓余暨权君时中曰。吾东方齿禊尚矣。下至牛医马卒。莫不以年甲携壶榼相从。流辈中年甲之同之多。莫如吾丙丁生。半生于百年。两日于一岁。尚不得与牛医马卒比。斯不亦耻之大者乎。况生长升平。忽涉乱离。寿夭不齐。死亡太半。盍及斯时。盛集吾齿甲而一欢耶。余等闻而矍然曰。谨图之。是年秋。再会于嘉仲兄第。有故不来者二人。亦有不速而会者总若干员。遂增损真率约束。斯非求多于古人。盖今古异宜而习俗不同也。约既定。嘉仲执盏言曰。斯甚盛会也。簿姓名。立约束。同樽俎。情义郑重。无以加矣。顾以禊帖无一语。恐或有指目而论之者。盍文之以解世之惑者。因共嘱任君卓尔。既又命余跋其尾。余辞不获。乃衍卓尔之意而为之言曰。昔文潞公
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04L 页
 为同甲会。绘像于资圣院。参斯会者。司马公,程公,席公也。同甲会。惟潞公外。前后无闻焉。年甲相厚。习也。古今所同。故人不表著耶。抑世之人。有行有不行。非俗所重。故无所传欤。是皆不敢知也。呜呼。世代迁革。习俗随变。事苟合宜。何必古也。彼兰亭之少长。香社之诸老。洛中之群英。是皆未得年齿之同者。姑取其气味之相似尔。若使更得一甲而禊之。其为乐。当何如耶。今余等。志未尝不合。道未尝不契。而加之以年齿之同。荀卿所谓贤友良友。而不杂以不善人者也。春畦撷嫩。秋水采鲜。寻花问柳。嘲风咏月。人皆有曲水之风。沂上之乐矣。醉饱之极。言或出入于诙谐。而物我两忘。俱为莫逆。彼既不知此之所是。此亦焉知彼之所非。时或有醒传者之云云。余恐未得其真是真非也。谚曰。生同甲。死同归。斯言也。固不可信其必然。余等姑尽其生前之欢尔。八公曰。水火相憎。䵻在其间。五味以和。骨肉相爱。谗贼间之而父子相危。余等毋为谗贼所间。必执䵻以和五味。闻者哄堂。谨书之。
为同甲会。绘像于资圣院。参斯会者。司马公,程公,席公也。同甲会。惟潞公外。前后无闻焉。年甲相厚。习也。古今所同。故人不表著耶。抑世之人。有行有不行。非俗所重。故无所传欤。是皆不敢知也。呜呼。世代迁革。习俗随变。事苟合宜。何必古也。彼兰亭之少长。香社之诸老。洛中之群英。是皆未得年齿之同者。姑取其气味之相似尔。若使更得一甲而禊之。其为乐。当何如耶。今余等。志未尝不合。道未尝不契。而加之以年齿之同。荀卿所谓贤友良友。而不杂以不善人者也。春畦撷嫩。秋水采鲜。寻花问柳。嘲风咏月。人皆有曲水之风。沂上之乐矣。醉饱之极。言或出入于诙谐。而物我两忘。俱为莫逆。彼既不知此之所是。此亦焉知彼之所非。时或有醒传者之云云。余恐未得其真是真非也。谚曰。生同甲。死同归。斯言也。固不可信其必然。余等姑尽其生前之欢尔。八公曰。水火相憎。䵻在其间。五味以和。骨肉相爱。谗贼间之而父子相危。余等毋为谗贼所间。必执䵻以和五味。闻者哄堂。谨书之。薛将军歌词跋
乐府歌词。昉于汉,魏。盛于唐,宋。即古诗言志依永之
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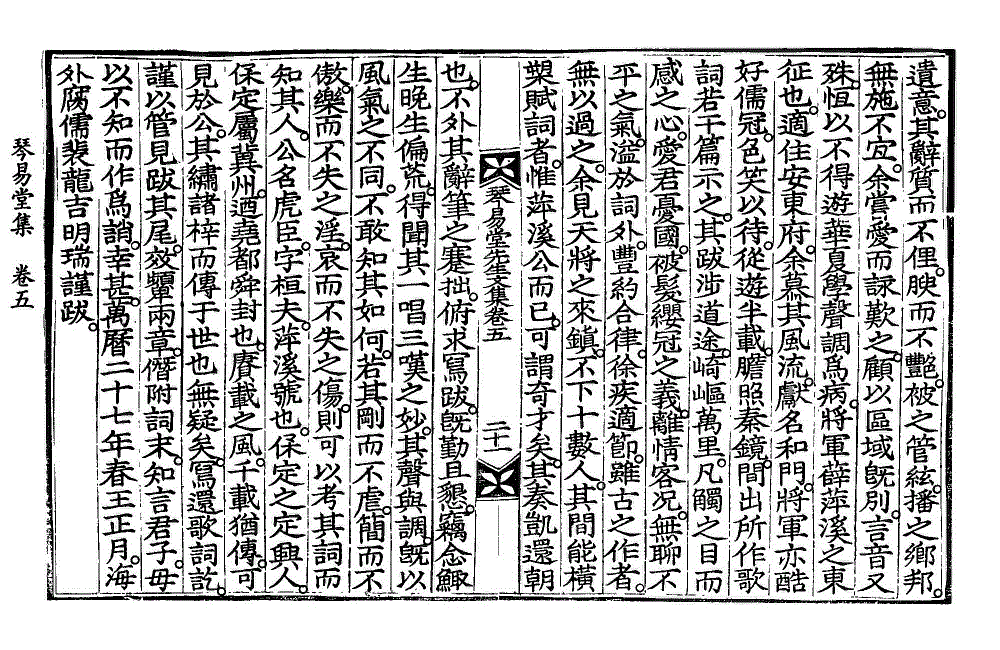 遗意。其辞质而不俚。腴而不艳。被之管弦。播之乡邦。无施不宜。余尝爱而咏叹之。顾以区域既别。言音又殊。恒以不得游华夏学声调为病。将军薛萍溪之东征也。适住安东府。余慕其风流。献名和门。将军亦酷好儒冠。色笑以待。从游半载。胆照秦镜。间出所作歌词若干篇示之。其跋涉道途。崎岖万里。凡触之目而感之心。爱君忧国。被发缨冠之义。离情客况。无聊不平之气。溢于词外。丰约合律。徐疾适节。虽古之作者。无以过之。余见天将之来镇。不下十数人。其间能横槊赋词者。惟萍溪公而已。可谓奇才矣。其奏凯还朝也。不外其辞笔之蹇拙。俯求写跋。既勤且恳。窃念鲰生晚生偏荒。得闻其一唱三叹之妙。其声与调。既以风气之不同。不敢知其如何。若其刚而不虐。简而不傲。乐而不失之淫。哀而不失之伤。则可以考其词而知其人。公名虎臣。字桓夫。萍溪号也。保定之定兴人。保定属冀州。乃尧都舜封也。赓载之风。千载犹传。可见于公。其绣诸梓而传于世也无疑矣。写还歌词讫。谨以管见跋其尾。效颦两章。僭附词末。知言君子。毋以不知而作为诮。幸甚。万历二十七年春王正月。海外腐儒裴龙吉明瑞谨跋。
遗意。其辞质而不俚。腴而不艳。被之管弦。播之乡邦。无施不宜。余尝爱而咏叹之。顾以区域既别。言音又殊。恒以不得游华夏学声调为病。将军薛萍溪之东征也。适住安东府。余慕其风流。献名和门。将军亦酷好儒冠。色笑以待。从游半载。胆照秦镜。间出所作歌词若干篇示之。其跋涉道途。崎岖万里。凡触之目而感之心。爱君忧国。被发缨冠之义。离情客况。无聊不平之气。溢于词外。丰约合律。徐疾适节。虽古之作者。无以过之。余见天将之来镇。不下十数人。其间能横槊赋词者。惟萍溪公而已。可谓奇才矣。其奏凯还朝也。不外其辞笔之蹇拙。俯求写跋。既勤且恳。窃念鲰生晚生偏荒。得闻其一唱三叹之妙。其声与调。既以风气之不同。不敢知其如何。若其刚而不虐。简而不傲。乐而不失之淫。哀而不失之伤。则可以考其词而知其人。公名虎臣。字桓夫。萍溪号也。保定之定兴人。保定属冀州。乃尧都舜封也。赓载之风。千载犹传。可见于公。其绣诸梓而传于世也无疑矣。写还歌词讫。谨以管见跋其尾。效颦两章。僭附词末。知言君子。毋以不知而作为诮。幸甚。万历二十七年春王正月。海外腐儒裴龙吉明瑞谨跋。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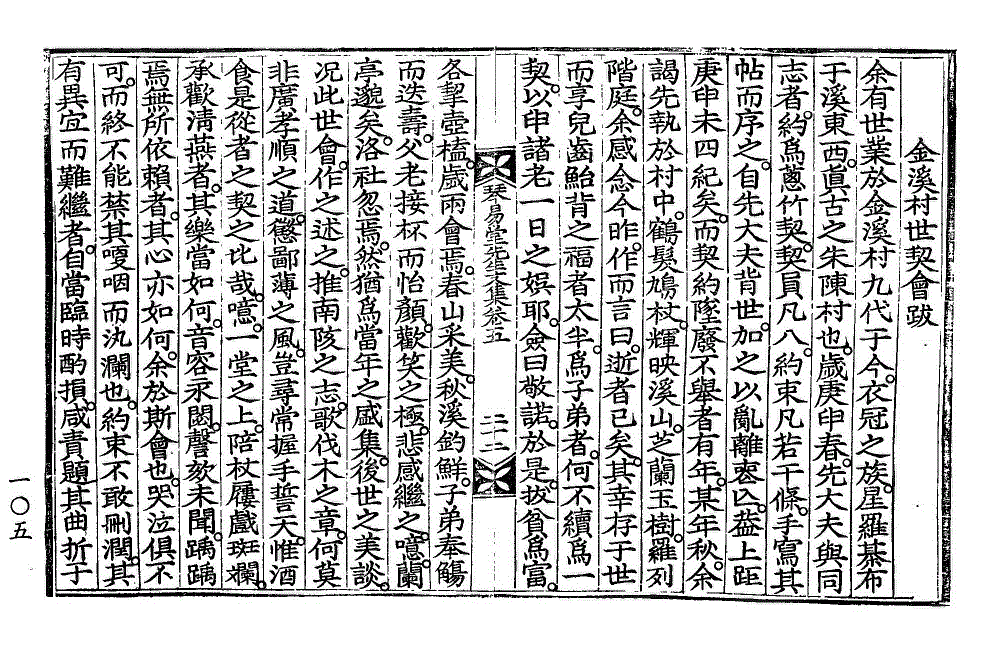 金溪村世契会跋
金溪村世契会跋余有世业于金溪村九代于今。衣冠之族。星罗棋布于溪东西。真古之朱陈村也。岁庚申春。先大夫与同志者。约为葱竹契。契员凡八。约束凡若干条。手写其帖而序之。自先大夫背世。加之以乱离丧亡。盖上距庚申未四纪矣。而契约坠废不举者有年。某年秋。余谒先执于村中。鹤发鸠杖。辉映溪山。芝兰玉树。罗列阶庭。余感念今昨。作而言曰。逝者已矣。其幸存于世而享儿齿鲐背之福者太半。为子弟者。何不续为一契。以申诸老一日之娱耶。佥曰敬诺。于是。拔贫为富。各挈壶榼。岁两会焉。春山采美。秋溪钓鲜。子弟奉觞而迭寿。父老接杯而怡颜。欢笑之极。悲感继之。噫。兰亭邈矣。洛社忽焉。然犹为当年之盛集。后世之美谈。况此世会。作之述之。推南陔之志。歌伐木之章。何莫非广孝顺之道。惩鄙薄之风。岂寻常握手誓天。惟酒食是从者之契之比哉。噫。一堂之上。陪杖屦戏斑斓。承欢清燕者。其乐当如何。音容永閟。謦欬未闻。踽踽焉无所依赖者。其心亦如何。余于斯会也。哭泣俱不可。而终不能禁其哽咽而汍澜也。约束不敢删润。其有异宜而难继者。自当临时酌损。咸责题其曲折于
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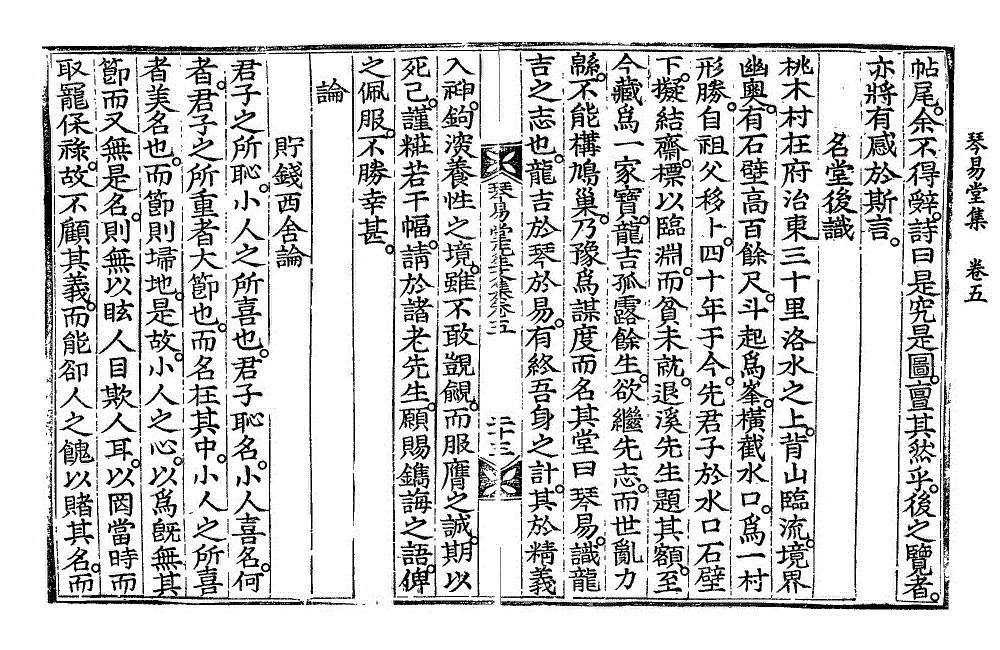 帖尾。余不得辞。诗曰是究是图。亶其然乎。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言。
帖尾。余不得辞。诗曰是究是图。亶其然乎。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言。名堂后识
桃木村在府治东三十里洛水之上。背山临流。境界幽奥。有石壁高百馀尺。斗起为峰。横截水口。为一村形胜。自祖父移卜。四十年于今。先君子于水口石壁下。拟结斋。标以临渊。而贫未就。退溪先生题其额。至今藏为一家宝。龙吉孤露馀生。欲继先志。而世乱力绵。不能构鸠巢。乃豫为谋度而名其堂曰琴易。识龙吉之志也。龙吉于琴于易。有终吾身之计。其于精义入神。钩深养性之境。虽不敢觊觎。而服膺之诚。期以死已。谨妆若干幅。请于诸老先生。愿赐镌诲之语。俾之佩服。不胜幸甚。
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论
贮钱西舍论
君子之所耻。小人之所喜也。君子耻名。小人喜名。何者。君子之所重者大节也。而名在其中。小人之所喜者美名也。而节则埽地。是故。小人之心。以为既无其节而又无是名。则无以眩人目欺人耳。以罔当时而取宠保禄。故不顾其义。而能却人之馈以赌其名。而
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06L 页
 不知君子之所鄙者。正在于此也。是故。善观人者。不于其小而于其大。不于其轻而于其重。噫。以名之小者与义之大者。奚啻义大。以廉之轻者与节之重者。奚啻节重。愚于刘温叟之贮钱西舍。窃甚鄙之。温叟。五季人也。在家而以孝母称。处乡而以好古闻。名重当时。誉流后世。闻其名则美矣。观其行则曾狗彘之不若也。温叟臣于唐。臣于晋。又臣于汉周及宋。则其于大节。无足观者。而谓贮钱为清慎者可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有礼义廉耻也。礼义廉耻。谓之四维。国而无此则亡。人而无此则禽兽矣。是故。无礼义之心。非人也。无廉耻之心。非人也。徒尚古人之糟粕者。谓之礼义之人可乎。徒辞时人之馈遗者。谓之廉耻之人可乎。况人生于三。事之如一。则视其国如逆旅。视其君如仇雠者。谓之礼义廉耻之人。尤不可也。生或可舍而其身不可辱也。义当可取而其节不可亏也。身而可辱者。为生不能舍也。节而可亏者。为义不能明也。义不明而生不舍。故喜名之心生而谋利之计作。自以为既不能致身于一君。而见讥于君子之人。则惟有曲谨小节。足以欺当时罔后世者。于是。清介以治身。方正以操心。曲拳擎跪。足以取礼法之
不知君子之所鄙者。正在于此也。是故。善观人者。不于其小而于其大。不于其轻而于其重。噫。以名之小者与义之大者。奚啻义大。以廉之轻者与节之重者。奚啻节重。愚于刘温叟之贮钱西舍。窃甚鄙之。温叟。五季人也。在家而以孝母称。处乡而以好古闻。名重当时。誉流后世。闻其名则美矣。观其行则曾狗彘之不若也。温叟臣于唐。臣于晋。又臣于汉周及宋。则其于大节。无足观者。而谓贮钱为清慎者可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有礼义廉耻也。礼义廉耻。谓之四维。国而无此则亡。人而无此则禽兽矣。是故。无礼义之心。非人也。无廉耻之心。非人也。徒尚古人之糟粕者。谓之礼义之人可乎。徒辞时人之馈遗者。谓之廉耻之人可乎。况人生于三。事之如一。则视其国如逆旅。视其君如仇雠者。谓之礼义廉耻之人。尤不可也。生或可舍而其身不可辱也。义当可取而其节不可亏也。身而可辱者。为生不能舍也。节而可亏者。为义不能明也。义不明而生不舍。故喜名之心生而谋利之计作。自以为既不能致身于一君。而见讥于君子之人。则惟有曲谨小节。足以欺当时罔后世者。于是。清介以治身。方正以操心。曲拳擎跪。足以取礼法之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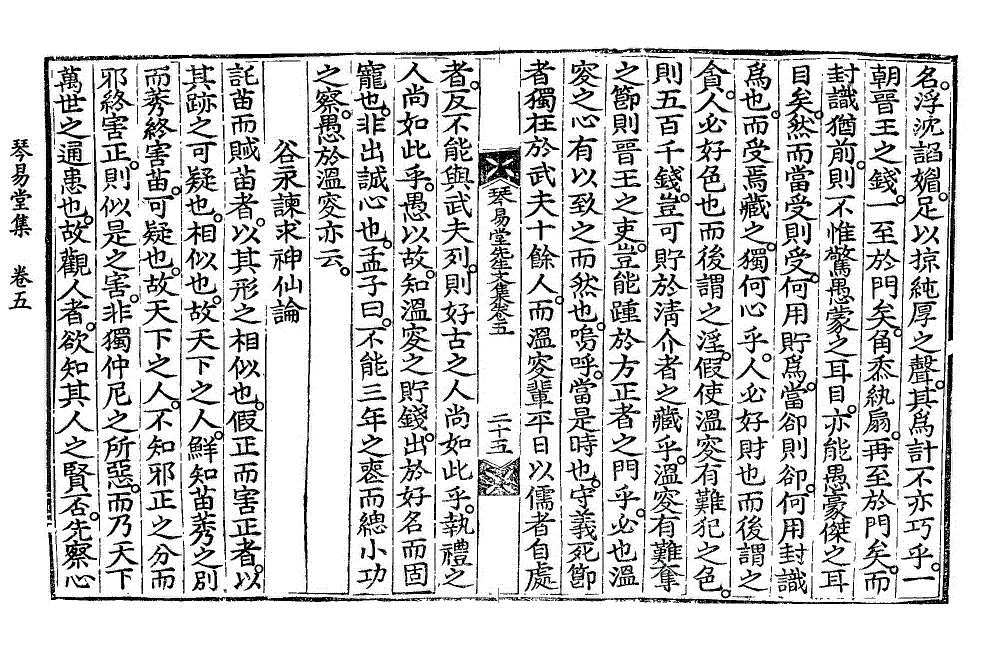 名。浮沈谄媚。足以掠纯厚之声。其为计不亦巧乎。一朝晋王之钱。一至于门矣。角忝纨扇。再至于门矣。而封识犹前。则不惟惊愚蒙之耳目。亦能愚豪杰之耳目矣。然而当受则受。何用贮为。当却则却。何用封识为也。而受焉藏之。独何心乎。人必好财也而后谓之贪。人必好色也而后谓之淫。假使温叟有难犯之色。则五百千钱。岂可贮于清介者之藏乎。温叟有难夺之节则晋王之吏。岂能踵于方正者之门乎。必也温叟之心有以致之而然也。呜呼。当是时也。守义死节者独在于武夫十馀人。而温叟辈平日以儒者自处者。反不能与武夫列。则好古之人尚如此乎。执礼之人尚如此乎。愚以故。知温叟之贮钱。出于好名而固宠也。非出诚心也。孟子曰。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愚于温叟亦云。
名。浮沈谄媚。足以掠纯厚之声。其为计不亦巧乎。一朝晋王之钱。一至于门矣。角忝纨扇。再至于门矣。而封识犹前。则不惟惊愚蒙之耳目。亦能愚豪杰之耳目矣。然而当受则受。何用贮为。当却则却。何用封识为也。而受焉藏之。独何心乎。人必好财也而后谓之贪。人必好色也而后谓之淫。假使温叟有难犯之色。则五百千钱。岂可贮于清介者之藏乎。温叟有难夺之节则晋王之吏。岂能踵于方正者之门乎。必也温叟之心有以致之而然也。呜呼。当是时也。守义死节者独在于武夫十馀人。而温叟辈平日以儒者自处者。反不能与武夫列。则好古之人尚如此乎。执礼之人尚如此乎。愚以故。知温叟之贮钱。出于好名而固宠也。非出诚心也。孟子曰。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愚于温叟亦云。谷永谏求神仙论
托苗而贼苗者。以其形之相似也。假正而害正者。以其迹之可疑也。相似也。故天下之人。鲜知苗莠之别而莠终害苗。可疑也。故天下之人。不知邪正之分而邪终害正。则似是之害。非独仲尼之所恶。而乃天下万世之通患也。故观人者。欲知其人之贤否。先察心
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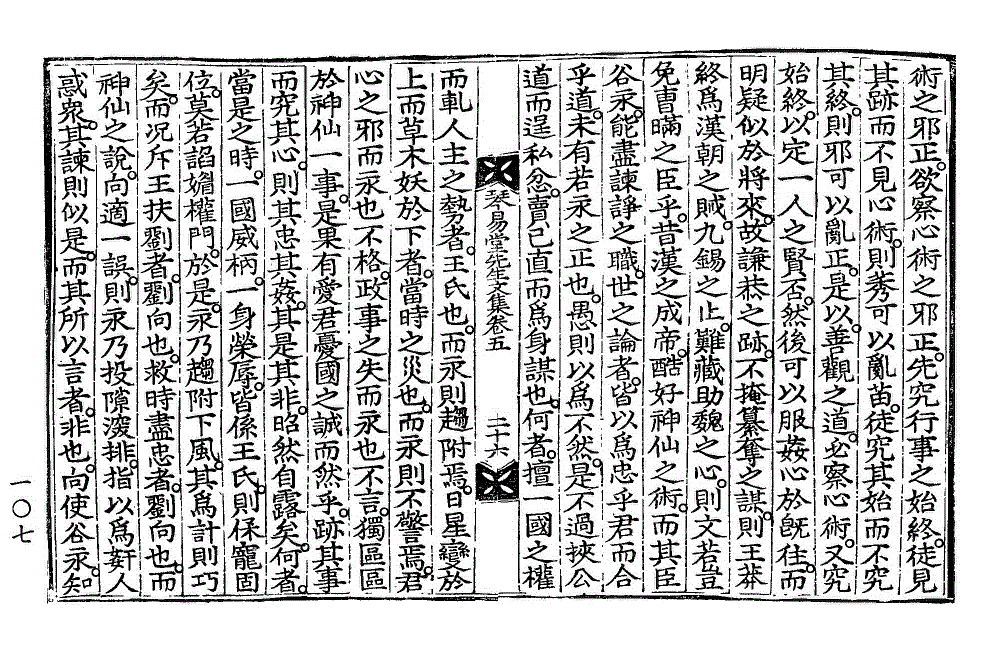 术之邪正。欲察心术之邪正。先究行事之始终。徒见其迹而不见心术。则莠可以乱苗。徒究其始而不究其终。则邪可以乱正。是以。善观之道。必察心术。又究始终。以定一人之贤否。然后可以服奸心于既往。而明疑似于将来。故谦恭之迹。不掩纂夺之谋。则王莽终为汉朝之贼。九锡之止。难臧助魏之心。则文若岂免曹瞒之臣乎。昔汉之成帝。酷好神仙之术。而其臣谷永。能尽谏诤之职。世之论者。皆以为忠乎君而合乎道。未有若永之正也。愚则以为不然。是不过挟公道而逞私忿。卖己直而为身谋也。何者。擅一国之权而轧人主之势者。王氏也。而永则趋附焉。日星变于上而草木妖于下者。当时之灾也。而永则不警焉。君心之邪而永也不格。政事之失而永也不言。独区区于神仙一事。是果有爱君忧国之诚而然乎。迹其事而究其心。则其忠其奸。其是其非。昭然自露矣。何者。当是之时。一国威柄。一身荣辱。皆系王氏。则保宠固位。莫若谄媚权门。于是。永乃趋附下风。其为计则巧矣。而况斥王扶刘者。刘向也。救时尽忠者。刘向也。而神仙之说。向适一误。则永乃投隙深排。指以为奸人惑众。其谏则似是。而其所以言者。非也。向使谷永。知
术之邪正。欲察心术之邪正。先究行事之始终。徒见其迹而不见心术。则莠可以乱苗。徒究其始而不究其终。则邪可以乱正。是以。善观之道。必察心术。又究始终。以定一人之贤否。然后可以服奸心于既往。而明疑似于将来。故谦恭之迹。不掩纂夺之谋。则王莽终为汉朝之贼。九锡之止。难臧助魏之心。则文若岂免曹瞒之臣乎。昔汉之成帝。酷好神仙之术。而其臣谷永。能尽谏诤之职。世之论者。皆以为忠乎君而合乎道。未有若永之正也。愚则以为不然。是不过挟公道而逞私忿。卖己直而为身谋也。何者。擅一国之权而轧人主之势者。王氏也。而永则趋附焉。日星变于上而草木妖于下者。当时之灾也。而永则不警焉。君心之邪而永也不格。政事之失而永也不言。独区区于神仙一事。是果有爱君忧国之诚而然乎。迹其事而究其心。则其忠其奸。其是其非。昭然自露矣。何者。当是之时。一国威柄。一身荣辱。皆系王氏。则保宠固位。莫若谄媚权门。于是。永乃趋附下风。其为计则巧矣。而况斥王扶刘者。刘向也。救时尽忠者。刘向也。而神仙之说。向适一误。则永乃投隙深排。指以为奸人惑众。其谏则似是。而其所以言者。非也。向使谷永。知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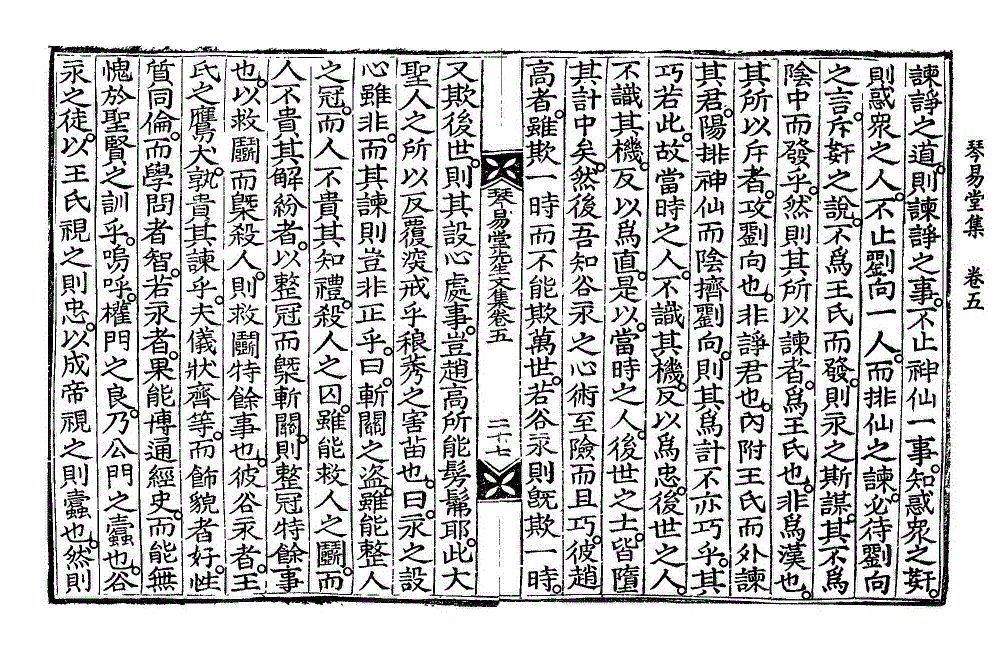 谏诤之道。则谏诤之事。不止神仙一事。知惑众之奸。则惑众之人。不止刘向一人。而排仙之谏。必待刘向之言。斥奸之说。不为王氏而发。则永之斯谋。其不为阴中而发乎。然则其所以谏者。为王氏也。非为汉也。其所以斥者。攻刘向也。非诤君也。内附王氏而外谏其君。阳排神仙而阴挤刘向。则其为计不亦巧乎。其巧若此。故当时之人。不识其机。反以为忠。后世之人。不识其机。反以为直。是以。当时之人。后世之士。皆堕其计中矣。然后吾知谷永之心术至险而且巧。彼赵高者。虽欺一时而不能欺万世。若谷永则既欺一时。又欺后世。则其设心处事。岂赵高所能髣髴耶。此大圣人之所以反覆深戒乎稂莠之害苗也。曰。永之设心虽非。而其谏则岂非正乎。曰。斩关之盗。虽能整人之冠。而人不贵其知礼。杀人之囚。虽能救人之斗。而人不贵其解纷者。以整冠而概斩关。则整冠特馀事也。以救斗而概杀人。则救斗特馀事也。彼谷永者。王氏之鹰犬。孰贵其谏乎。夫仪状齐等。而饰貌者好。性质同伦。而学问者智。若永者。果能博通经史。而能无愧于圣贤之训乎。呜呼。权门之良。乃公门之蠹也。谷永之徒。以王氏视之则忠。以成帝视之则蠹也。然则
谏诤之道。则谏诤之事。不止神仙一事。知惑众之奸。则惑众之人。不止刘向一人。而排仙之谏。必待刘向之言。斥奸之说。不为王氏而发。则永之斯谋。其不为阴中而发乎。然则其所以谏者。为王氏也。非为汉也。其所以斥者。攻刘向也。非诤君也。内附王氏而外谏其君。阳排神仙而阴挤刘向。则其为计不亦巧乎。其巧若此。故当时之人。不识其机。反以为忠。后世之人。不识其机。反以为直。是以。当时之人。后世之士。皆堕其计中矣。然后吾知谷永之心术至险而且巧。彼赵高者。虽欺一时而不能欺万世。若谷永则既欺一时。又欺后世。则其设心处事。岂赵高所能髣髴耶。此大圣人之所以反覆深戒乎稂莠之害苗也。曰。永之设心虽非。而其谏则岂非正乎。曰。斩关之盗。虽能整人之冠。而人不贵其知礼。杀人之囚。虽能救人之斗。而人不贵其解纷者。以整冠而概斩关。则整冠特馀事也。以救斗而概杀人。则救斗特馀事也。彼谷永者。王氏之鹰犬。孰贵其谏乎。夫仪状齐等。而饰貌者好。性质同伦。而学问者智。若永者。果能博通经史。而能无愧于圣贤之训乎。呜呼。权门之良。乃公门之蠹也。谷永之徒。以王氏视之则忠。以成帝视之则蠹也。然则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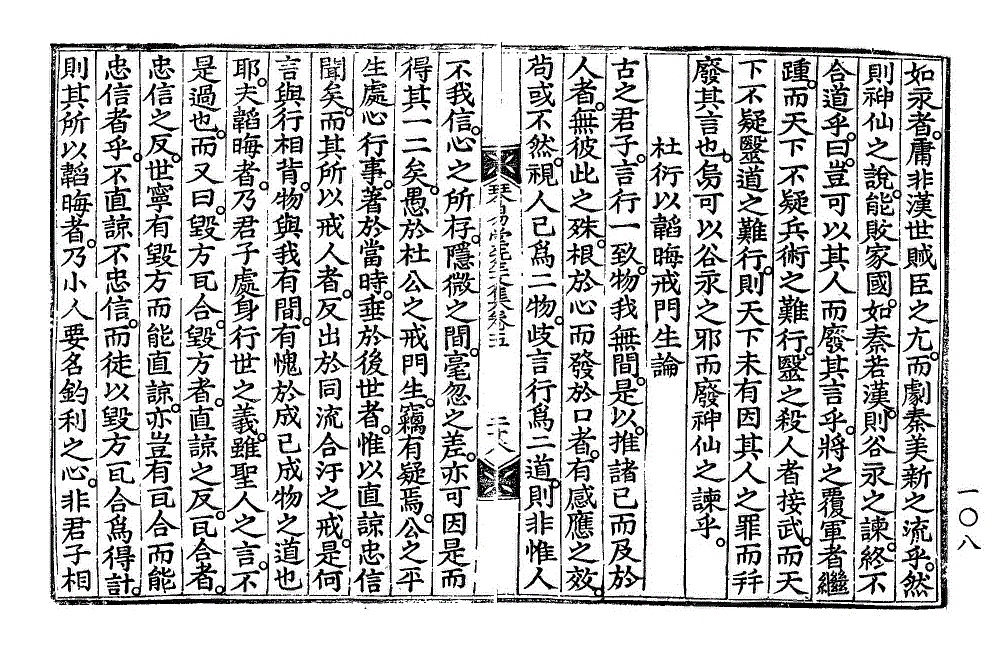 如永者。庸非汉世贼臣之尤。而剧秦美新之流乎。然则神仙之说。能败家国。如秦若汉。则谷永之谏。终不合道乎。曰。岂可以其人而废其言乎。将之覆军者继踵。而天下不疑兵术之难行。医之杀人者接武。而天下不疑医道之难行。则天下未有因其人之罪而并废其言也。乌可以谷永之邪而废神仙之谏乎。
如永者。庸非汉世贼臣之尤。而剧秦美新之流乎。然则神仙之说。能败家国。如秦若汉。则谷永之谏。终不合道乎。曰。岂可以其人而废其言乎。将之覆军者继踵。而天下不疑兵术之难行。医之杀人者接武。而天下不疑医道之难行。则天下未有因其人之罪而并废其言也。乌可以谷永之邪而废神仙之谏乎。杜衍以韬晦戒门生论
古之君子。言行一致。物我无间。是以。推诸己而及于人者。无彼此之殊。根于心而发于口者。有感应之效。苟或不然。视人己为二物。岐言行为二道。则非惟人不我信。心之所存。隐微之间。毫忽之差。亦可因是而得其一二矣。愚于杜公之戒门生。窃有疑焉。公之平生处心行事。著于当时。垂于后世者。惟以直谅忠信闻矣。而其所以戒人者。反出于同流合污之戒。是何言与行相背。物与我有间。有愧于成己成物之道也耶。夫韬晦者。乃君子处身行世之义。虽圣人之言。不是过也。而又曰。毁方瓦合。毁方者。直谅之反。瓦合者。忠信之反。世宁有毁方而能直谅。亦岂有瓦合而能忠信者乎。不直谅不忠信。而徒以毁方瓦合为得计。则其所以韬晦者。乃小人要名钓利之心。非君子相
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09H 页
 时度宜之道也。公之所言。何其与所行而戾。公之自为。何其与诲人而违也。然则公之平日以直谅闻者。非出于至公自然之本心。实乃假此而欲取名于当时者也。夫有是根则有是枝叶。有是源则有是流派。虽谓公之所言。不根于心。公之待物。不异于己。愚不信也。况祸福之虑。尤非君子之所及。利害当前而苟顾祸福。则居人下而能尽其心者。有几人哉。上下之分。虽有大小。其所以事之者。顾岂有二耶。小而事长吏。顾祸福而为祸福之计。则大而事君父。宁尽忠谅之心乎。使公不遇仁宗之圣。则必不以直谅闻。而反以毁方闻。使公不遇韩,范之友。则必不以忠信闻。而反以瓦合闻矣。中之为道。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当直谅而直谅。乃是中也。当直谅而毁方。岂是中乎。当忠信而忠信。乃是中也。当忠信而瓦合。岂是中乎。事长吏尽其直谅忠信之心。乃得为中也。如或不遇则有去而已。岂毁方瓦合。隐忍眷恋。而能不失其本心之中乎。然则公之所谓中者。乃恋爵保禄。小人之尤甚者。如是而能合于无过不及之中乎。此愚所以二言行。间物我。深为杜公之病者也。或曰。然则祁公之齿于韩,范。无乃太史曲笔乎。曰。公之尽事君之职
时度宜之道也。公之所言。何其与所行而戾。公之自为。何其与诲人而违也。然则公之平日以直谅闻者。非出于至公自然之本心。实乃假此而欲取名于当时者也。夫有是根则有是枝叶。有是源则有是流派。虽谓公之所言。不根于心。公之待物。不异于己。愚不信也。况祸福之虑。尤非君子之所及。利害当前而苟顾祸福。则居人下而能尽其心者。有几人哉。上下之分。虽有大小。其所以事之者。顾岂有二耶。小而事长吏。顾祸福而为祸福之计。则大而事君父。宁尽忠谅之心乎。使公不遇仁宗之圣。则必不以直谅闻。而反以毁方闻。使公不遇韩,范之友。则必不以忠信闻。而反以瓦合闻矣。中之为道。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当直谅而直谅。乃是中也。当直谅而毁方。岂是中乎。当忠信而忠信。乃是中也。当忠信而瓦合。岂是中乎。事长吏尽其直谅忠信之心。乃得为中也。如或不遇则有去而已。岂毁方瓦合。隐忍眷恋。而能不失其本心之中乎。然则公之所谓中者。乃恋爵保禄。小人之尤甚者。如是而能合于无过不及之中乎。此愚所以二言行。间物我。深为杜公之病者也。或曰。然则祁公之齿于韩,范。无乃太史曲笔乎。曰。公之尽事君之职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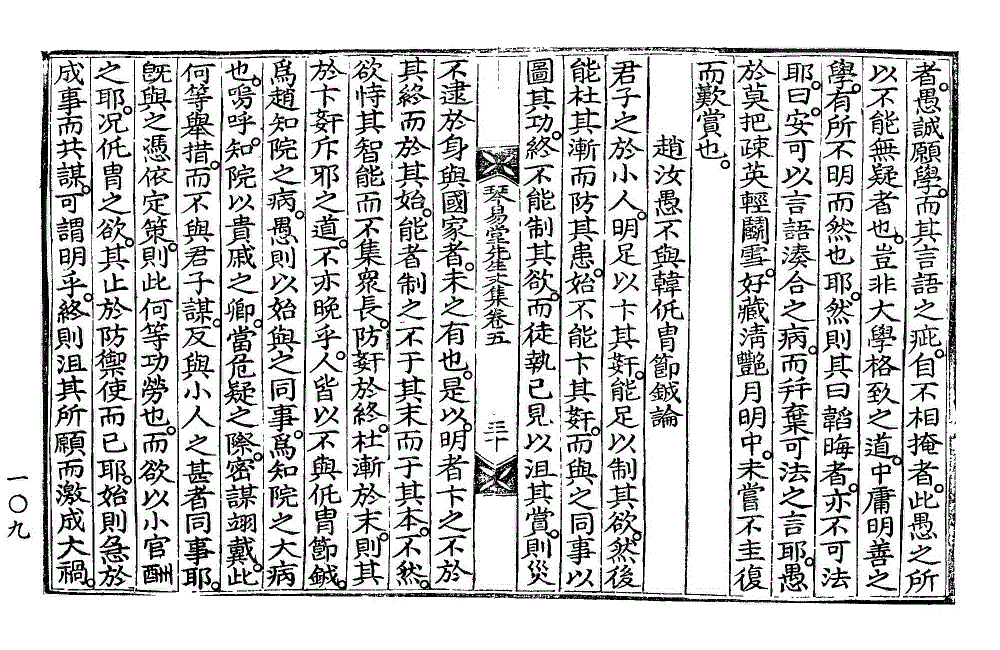 者。愚诚愿学。而其言语之疵。自不相掩者。此愚之所以不能无疑者也。岂非大学格致之道。中庸明善之学。有所不明而然也耶。然则其曰韬晦者。亦不可法耶。曰。安可以言语凑合之病。而并弃可法之言耶。愚于莫把疏英轻斗雪。好藏清艳月明中。未尝不圭复而叹赏也。
者。愚诚愿学。而其言语之疵。自不相掩者。此愚之所以不能无疑者也。岂非大学格致之道。中庸明善之学。有所不明而然也耶。然则其曰韬晦者。亦不可法耶。曰。安可以言语凑合之病。而并弃可法之言耶。愚于莫把疏英轻斗雪。好藏清艳月明中。未尝不圭复而叹赏也。赵汝愚不与韩侂胄节钺论
君子之于小人。明足以卞其奸。能足以制其欲。然后能杜其渐而防其患。始不能卞其奸。而与之同事以图其功。终不能制其欲。而徒执己见以沮其赏。则灾不逮于身与国家者。未之有也。是以。明者卞之不于其终而于其始。能者制之不于其末而于其本。不然。欲恃其智能而不集众长。防奸于终。杜渐于末。则其于卞奸斥邪之道。不亦晚乎。人皆以不与侂胄节钺。为赵知院之病。愚则以始与之同事。为知院之大病也。呜呼。知院以贵戚之卿。当危疑之际。密谋翊戴。此何等举措。而不与君子谋。反与小人之甚者同事耶。既与之凭依定策。则此何等功劳也。而欲以小官酬之耶。况侂胄之欲。其止于防御使而已耶。始则急于成事而共谋。可谓明乎。终则沮其所愿而激成大祸。
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0H 页
 可谓能乎。知院徒知达坤听济己志。非此人不可。而不知此人得志之后。己之能不能制之也。愚以为障洪川者。不障其流而障其源。伐恶木者。不伐其枝而伐其根。知院不知己之能不能制侂胄之奸。而欲禁其一节一钺于事成之后。不亦难乎。徒能激其怨而添其祸也已。及其奸谋已售。左腹明夷。则今年不与节钺。而明年兼枢密院都承旨矣。又明年。加保宁军节度使矣。必至于封郡王加太师而后已。则可谓不与节钺。能禁侂胄异日之奸乎。所以终之不与节钺。不若始之不与同事之为愈也。或曰。当是时。光宗病亟。相逃人散。庙谟危疑。国势岌岌。使知院既知侂胄之奸。则始既与之同事。终不与之节钺。以智则明。以事则正。何可深责。愚曰。屈寸而伸尺。圣人不为。小枉而大直。贤者耻之。与其正之于终。孰若正之于始。与其杜之于后。孰若杜之于前。是以。诡遇获禽。君子不贵。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故不以不与节钺。为知院之病。而以始与之同事。为知院之大病也。
可谓能乎。知院徒知达坤听济己志。非此人不可。而不知此人得志之后。己之能不能制之也。愚以为障洪川者。不障其流而障其源。伐恶木者。不伐其枝而伐其根。知院不知己之能不能制侂胄之奸。而欲禁其一节一钺于事成之后。不亦难乎。徒能激其怨而添其祸也已。及其奸谋已售。左腹明夷。则今年不与节钺。而明年兼枢密院都承旨矣。又明年。加保宁军节度使矣。必至于封郡王加太师而后已。则可谓不与节钺。能禁侂胄异日之奸乎。所以终之不与节钺。不若始之不与同事之为愈也。或曰。当是时。光宗病亟。相逃人散。庙谟危疑。国势岌岌。使知院既知侂胄之奸。则始既与之同事。终不与之节钺。以智则明。以事则正。何可深责。愚曰。屈寸而伸尺。圣人不为。小枉而大直。贤者耻之。与其正之于终。孰若正之于始。与其杜之于后。孰若杜之于前。是以。诡遇获禽。君子不贵。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故不以不与节钺。为知院之病。而以始与之同事。为知院之大病也。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辨
郑仁弘南冥集跋语辨
余闻郑仁弘为江右巨擘者有年。未知其言行之实
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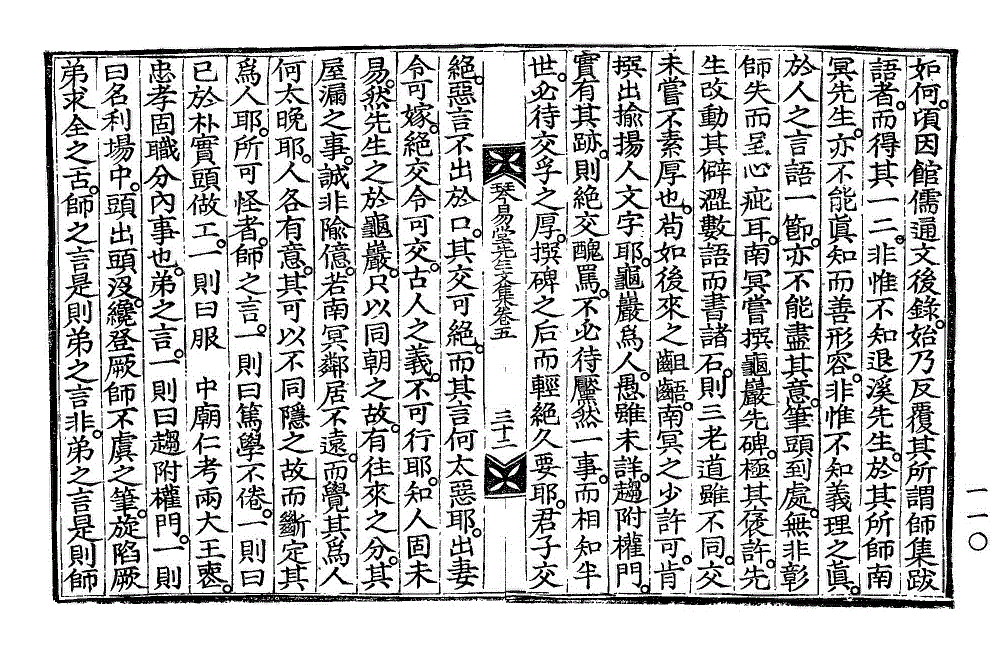 如何。顷因馆儒通文后录。始乃反覆其所谓师集跋语者。而得其一二。非惟不知退溪先生。于其所师南冥先生。亦不能真知而善形容。非惟不知义理之真。于人之言语一节。亦不能尽其意。笔头到处。无非彰师失而呈心疵耳。南冥尝撰龟岩先碑。极其褒许。先生改动其僻涩数语而书诸石。则三老道虽不同。交未尝不素厚也。苟如后来之龃龉。南冥之少许可。肯撰出揄扬人文字耶。龟岩为人。愚虽未详。趋附权门。实有其迹。则绝交丑骂。不必待黡然一事。而相知半世。必待交孚之厚。撰碑之后而轻绝久要耶。君子交绝。恶言不出于口。其交可绝。而其言何太恶耶。出妻令可嫁。绝交令可交。古人之义。不可行耶。知人固未易。然先生之于龟岩。只以同朝之故。有往来之分。其屋漏之事。诚非隃亿。若南冥邻居不远。而觉其为人何太晚耶。人各有意。其可以不同隐之故而断定其为人耶。所可怪者。师之言。一则曰笃学不倦。一则曰己于朴实头做工。一则曰服 中庙仁考两大王丧。忠孝固职分内事也。弟之言。一则曰趋附权门。一则曰名利场中。头出头没。才登厥师不虞之笔。旋陷厥弟求全之舌。师之言是则弟之言非。弟之言是则师
如何。顷因馆儒通文后录。始乃反覆其所谓师集跋语者。而得其一二。非惟不知退溪先生。于其所师南冥先生。亦不能真知而善形容。非惟不知义理之真。于人之言语一节。亦不能尽其意。笔头到处。无非彰师失而呈心疵耳。南冥尝撰龟岩先碑。极其褒许。先生改动其僻涩数语而书诸石。则三老道虽不同。交未尝不素厚也。苟如后来之龃龉。南冥之少许可。肯撰出揄扬人文字耶。龟岩为人。愚虽未详。趋附权门。实有其迹。则绝交丑骂。不必待黡然一事。而相知半世。必待交孚之厚。撰碑之后而轻绝久要耶。君子交绝。恶言不出于口。其交可绝。而其言何太恶耶。出妻令可嫁。绝交令可交。古人之义。不可行耶。知人固未易。然先生之于龟岩。只以同朝之故。有往来之分。其屋漏之事。诚非隃亿。若南冥邻居不远。而觉其为人何太晚耶。人各有意。其可以不同隐之故而断定其为人耶。所可怪者。师之言。一则曰笃学不倦。一则曰己于朴实头做工。一则曰服 中庙仁考两大王丧。忠孝固职分内事也。弟之言。一则曰趋附权门。一则曰名利场中。头出头没。才登厥师不虞之笔。旋陷厥弟求全之舌。师之言是则弟之言非。弟之言是则师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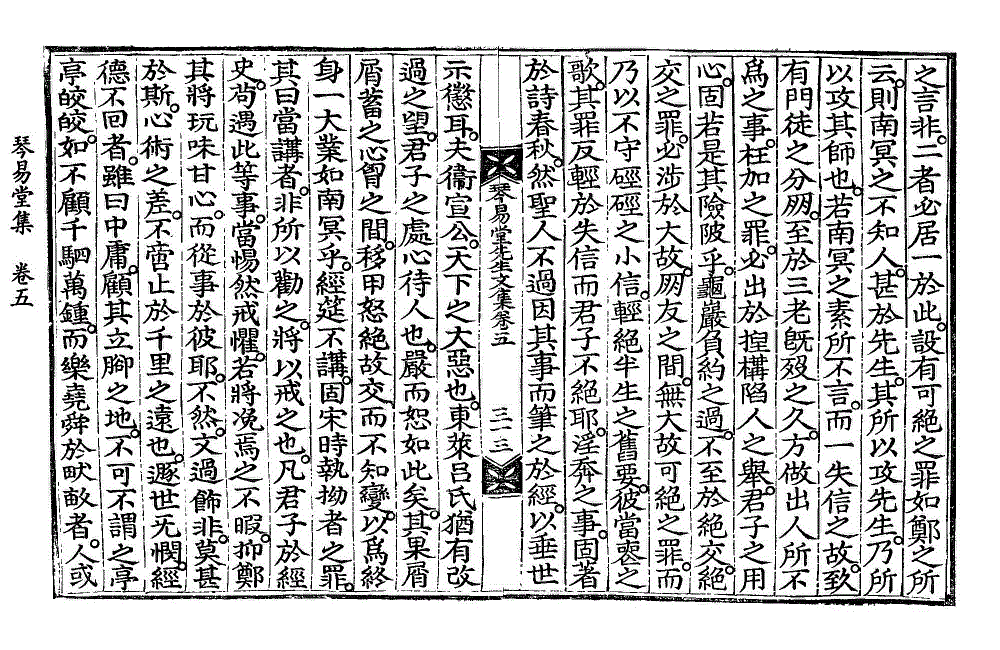 之言非。二者必居一于此。设有可绝之罪如郑之所云。则南冥之不知人。甚于先生。其所以攻先生。乃所以攻其师也。若南冥之素所不言。而一失信之故。致有门徒之分朋。至于三老既殁之久。方做出人所不为之事。枉加之罪。必出于捏构陷人之举。君子之用心。固若是其险陂乎。龟岩负约之过。不至于绝交。绝交之罪。必涉于大故。朋友之间。无大故可绝之罪。而乃以不守硁硁之小信。轻绝半生之旧要。彼当丧之歌。其罪反轻于失信而君子不绝耶。淫奔之事。固著于诗春秋。然圣人不过因其事而笔之于经。以垂世示惩耳。夫卫宣公。天下之大恶也。东莱吕氏犹有改过之望。君子之处心待人也。严而恕如此矣。其果屑屑蓄之心胸之间。移甲怒绝故交而不知变。以为终身一大业如南冥乎。经筵不讲。固宋时执拗者之罪。其曰当讲者。非所以劝之。将以戒之也。凡君子于经史。苟遇此等事。当惕然戒惧。若将浼焉之不暇。抑郑其将玩味甘心。而从事于彼耶。不然。文过饰非。莫甚于斯。心术之差。不啻止于千里之远也。遁世无悯。经德不回者。虽曰中庸。顾其立脚之地。不可不谓之亭亭皎皎。如不顾千驷万钟。而乐尧舜于畎亩者。人或
之言非。二者必居一于此。设有可绝之罪如郑之所云。则南冥之不知人。甚于先生。其所以攻先生。乃所以攻其师也。若南冥之素所不言。而一失信之故。致有门徒之分朋。至于三老既殁之久。方做出人所不为之事。枉加之罪。必出于捏构陷人之举。君子之用心。固若是其险陂乎。龟岩负约之过。不至于绝交。绝交之罪。必涉于大故。朋友之间。无大故可绝之罪。而乃以不守硁硁之小信。轻绝半生之旧要。彼当丧之歌。其罪反轻于失信而君子不绝耶。淫奔之事。固著于诗春秋。然圣人不过因其事而笔之于经。以垂世示惩耳。夫卫宣公。天下之大恶也。东莱吕氏犹有改过之望。君子之处心待人也。严而恕如此矣。其果屑屑蓄之心胸之间。移甲怒绝故交而不知变。以为终身一大业如南冥乎。经筵不讲。固宋时执拗者之罪。其曰当讲者。非所以劝之。将以戒之也。凡君子于经史。苟遇此等事。当惕然戒惧。若将浼焉之不暇。抑郑其将玩味甘心。而从事于彼耶。不然。文过饰非。莫甚于斯。心术之差。不啻止于千里之远也。遁世无悯。经德不回者。虽曰中庸。顾其立脚之地。不可不谓之亭亭皎皎。如不顾千驷万钟。而乐尧舜于畎亩者。人或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1L 页
 加之以此言。为子弟者闻之。必以为知言。不勃然发怒如郑也。古人多有断章取义者。以稚圭而用诸彦伦则为嘲侮。以君子而用之朋流则为平实。如为富不仁之谈。阳虎口之则为贼仁。孟子引之则为劝仁。况此数语。实有光于南冥者乎。南冥有隐德不仕之名。龟岩有仕宦显荣之名。名之于出与处也。何殊观耶。必欲以隐者为名流。而仕宦者不得为名流。则皋,夔,伊,吕不为名流。而老,庄,释氏方为名流也。孟子虽不见诸侯。诸侯有礼以先之。亦未尝不答。何尝有踰垣闭门过甚之举。至如庄光之伦。虽有先儒之云云。实以汉季之有此人为贵耳。非以为实有德业无愧于伊,吕也。今乃径处厥师于庄光之列。而欲免一节之名。不知类甚矣。夫以南冥一生辛苦工夫。不愧于为己之学。终揆以厥弟之言。其为事物所累。不能洒然无一事是当合于古人之迹。南冥不至于圣人地位。然窃恐其不应若是之甚也。若吾退溪先生则异于是。其处心也谦。其待人也忠。其与曹徵君一书。足以备见之矣。至于论道则继往开来。不可不严。故言语书尺。必柝秋毫。以求至当之归。仕止隐见。必务合义。以求吾心之安。其言行气象。出处行藏。自与南冥
加之以此言。为子弟者闻之。必以为知言。不勃然发怒如郑也。古人多有断章取义者。以稚圭而用诸彦伦则为嘲侮。以君子而用之朋流则为平实。如为富不仁之谈。阳虎口之则为贼仁。孟子引之则为劝仁。况此数语。实有光于南冥者乎。南冥有隐德不仕之名。龟岩有仕宦显荣之名。名之于出与处也。何殊观耶。必欲以隐者为名流。而仕宦者不得为名流。则皋,夔,伊,吕不为名流。而老,庄,释氏方为名流也。孟子虽不见诸侯。诸侯有礼以先之。亦未尝不答。何尝有踰垣闭门过甚之举。至如庄光之伦。虽有先儒之云云。实以汉季之有此人为贵耳。非以为实有德业无愧于伊,吕也。今乃径处厥师于庄光之列。而欲免一节之名。不知类甚矣。夫以南冥一生辛苦工夫。不愧于为己之学。终揆以厥弟之言。其为事物所累。不能洒然无一事是当合于古人之迹。南冥不至于圣人地位。然窃恐其不应若是之甚也。若吾退溪先生则异于是。其处心也谦。其待人也忠。其与曹徵君一书。足以备见之矣。至于论道则继往开来。不可不严。故言语书尺。必柝秋毫。以求至当之归。仕止隐见。必务合义。以求吾心之安。其言行气象。出处行藏。自与南冥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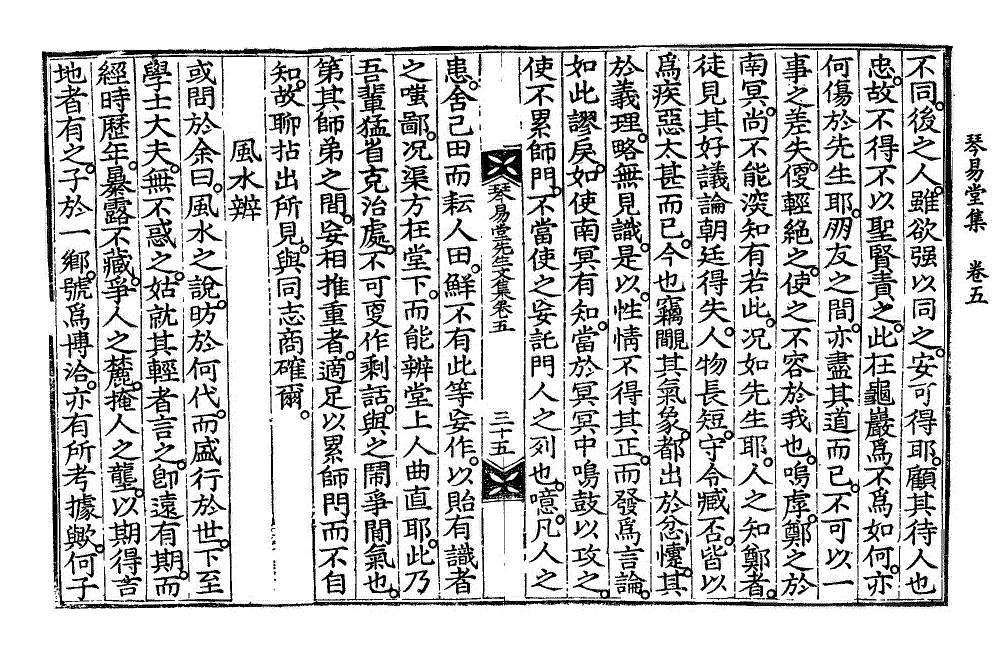 不同。后之人。虽欲强以同之。安可得耶。顾其待人也忠。故不得不以圣贤责之。此在龟岩为不为如何。亦何伤于先生耶。朋友之间。亦尽其道而已。不可以一事之差失。便轻绝之。使之不容于我也。呜虖。郑之于南冥。尚不能深知有若此。况如先生耶。人之知郑者。徒见其好议论朝廷得失。人物长短。守令臧否。皆以为疾恶太甚而已。今也窃覸其气象。都出于忿懥。其于义理。略无见识。是以。性情不得其正。而发为言论。如此谬戾。如使南冥有知。当于冥冥中鸣鼓以攻之。使不累师门。不当使之妄托门人之列也。噫。凡人之患。舍己田而耘人田。鲜不有此等妄作。以贻有识者之嗤鄙。况渠方在堂下。而能辨堂上人曲直耶。此乃吾辈猛省克治处。不可更作剩话。与之闹争閒气也。第其师弟之间。妄相推重者。适足以累师门而不自知。故聊拈出所见。与同志商确尔。
不同。后之人。虽欲强以同之。安可得耶。顾其待人也忠。故不得不以圣贤责之。此在龟岩为不为如何。亦何伤于先生耶。朋友之间。亦尽其道而已。不可以一事之差失。便轻绝之。使之不容于我也。呜虖。郑之于南冥。尚不能深知有若此。况如先生耶。人之知郑者。徒见其好议论朝廷得失。人物长短。守令臧否。皆以为疾恶太甚而已。今也窃覸其气象。都出于忿懥。其于义理。略无见识。是以。性情不得其正。而发为言论。如此谬戾。如使南冥有知。当于冥冥中鸣鼓以攻之。使不累师门。不当使之妄托门人之列也。噫。凡人之患。舍己田而耘人田。鲜不有此等妄作。以贻有识者之嗤鄙。况渠方在堂下。而能辨堂上人曲直耶。此乃吾辈猛省克治处。不可更作剩话。与之闹争閒气也。第其师弟之间。妄相推重者。适足以累师门而不自知。故聊拈出所见。与同志商确尔。风水辨
或问于余曰。风水之说。昉于何代。而盛行于世。下至学士大夫。无不惑之。姑就其轻者言之。即远有期。而经时历年。暴露不臧。争人之麓。掩人之垄。以期得吉地者有之。子于一乡。号为博洽。亦有所考据欤。何子
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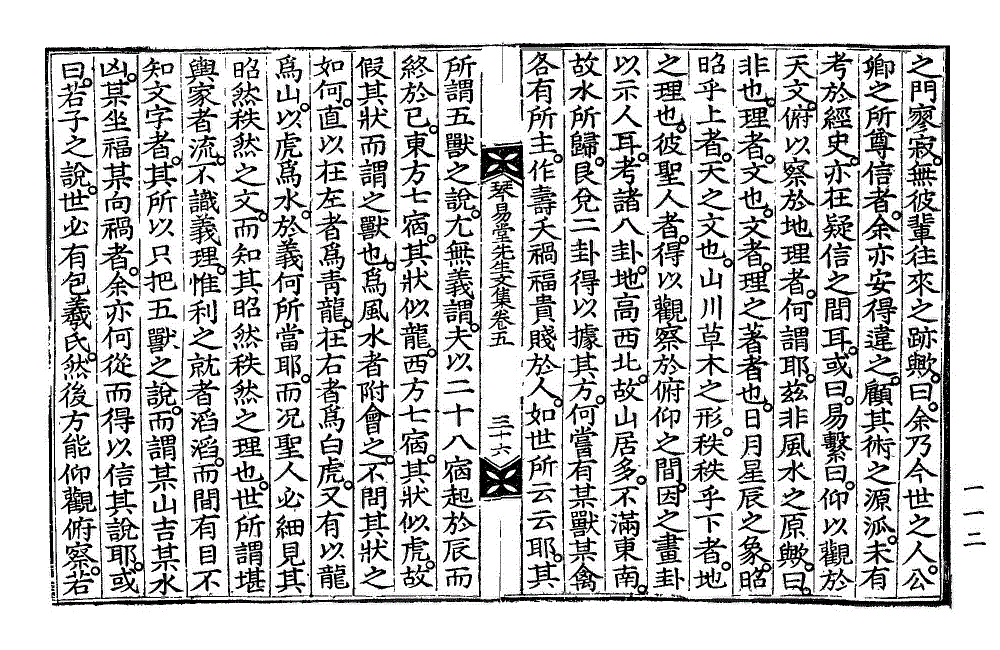 之门寥寂。无彼辈往来之迹欤。曰。余乃今世之人。公卿之所尊信者。余亦安得违之。顾其术之源派。未有考于经史。亦在疑信之间耳。或曰。易系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者。何谓耶。玆非风水之原欤。曰。非也。理者。文也。文者。理之著者也。日月星辰之象。昭昭乎上者。天之文也。山川草木之形。秩秩乎下者。地之理也。彼圣人者。得以观察于俯仰之间。因之画卦以示人耳。考诸八卦。地高西北。故山居多。不满东南。故水所归。艮兑二卦得以据其方。何尝有某兽某禽各有所主。作寿夭祸福贵贱于人。如世所云云耶。其所谓五兽之说。尤无义谓。夫以二十八宿起于辰而终于巳。东方七宿。其状似龙。西方七宿。其状似虎。故假其状而谓之兽也。为风水者附会之。不问其状之如何。直以在左者为青龙。在右者为白虎。又有以龙为山。以虎为水。于义何所当耶。而况圣人必细见其昭然秩然之文。而知其昭然秩然之理也。世所谓堪舆家者流。不识义理。惟利之就者滔滔。而间有目不知文字者。其所以只把五兽之说。而谓某山吉某水凶。某坐福某向祸者。余亦何从而得以信其说耶。或曰。若子之说。世必有包羲氏。然后方能仰观俯察。若
之门寥寂。无彼辈往来之迹欤。曰。余乃今世之人。公卿之所尊信者。余亦安得违之。顾其术之源派。未有考于经史。亦在疑信之间耳。或曰。易系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者。何谓耶。玆非风水之原欤。曰。非也。理者。文也。文者。理之著者也。日月星辰之象。昭昭乎上者。天之文也。山川草木之形。秩秩乎下者。地之理也。彼圣人者。得以观察于俯仰之间。因之画卦以示人耳。考诸八卦。地高西北。故山居多。不满东南。故水所归。艮兑二卦得以据其方。何尝有某兽某禽各有所主。作寿夭祸福贵贱于人。如世所云云耶。其所谓五兽之说。尤无义谓。夫以二十八宿起于辰而终于巳。东方七宿。其状似龙。西方七宿。其状似虎。故假其状而谓之兽也。为风水者附会之。不问其状之如何。直以在左者为青龙。在右者为白虎。又有以龙为山。以虎为水。于义何所当耶。而况圣人必细见其昭然秩然之文。而知其昭然秩然之理也。世所谓堪舆家者流。不识义理。惟利之就者滔滔。而间有目不知文字者。其所以只把五兽之说。而谓某山吉某水凶。某坐福某向祸者。余亦何从而得以信其说耶。或曰。若子之说。世必有包羲氏。然后方能仰观俯察。若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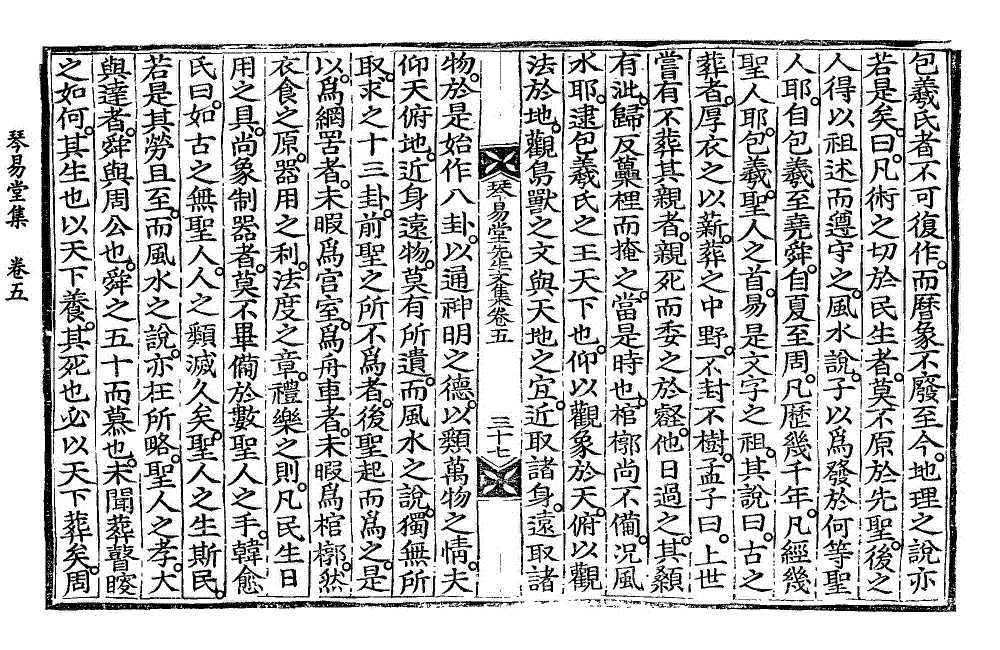 包羲氏者不可复作。而历象不废至今。地理之说亦若是矣。曰。凡术之切于民生者。莫不原于先圣。后之人得以祖述而遵守之。风水说。子以为发于何等圣人耶。自包羲至尧舜。自夏至周。凡历几千年。凡经几圣人耶。包羲。圣人之首。易是文字之祖。其说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孟子曰。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亲死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其颡有泚。归反藟梩而掩之。当是时也。棺椁尚不备。况风水耶。逮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观象于天。俯以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天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夫仰天俯地。近身远物。莫有所遗。而风水之说。独无所取。求之十三卦。前圣之所不为者。后圣起而为之。是以。为网罟者。未暇为宫室。为舟车者。未暇为棺椁。然衣食之原。器用之利。法度之章。礼乐之则。凡民生日用之具。尚象制器者。莫不毕备于数圣人之手。韩愈氏曰。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圣人之生斯民。若是其劳且至。而风水之说。亦在所略。圣人之孝。大与达者。舜与周公也。舜之五十而慕也。未闻葬瞽瞍之如何。其生也以天下养。其死也必以天下葬矣。周
包羲氏者不可复作。而历象不废至今。地理之说亦若是矣。曰。凡术之切于民生者。莫不原于先圣。后之人得以祖述而遵守之。风水说。子以为发于何等圣人耶。自包羲至尧舜。自夏至周。凡历几千年。凡经几圣人耶。包羲。圣人之首。易是文字之祖。其说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孟子曰。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亲死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其颡有泚。归反藟梩而掩之。当是时也。棺椁尚不备。况风水耶。逮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观象于天。俯以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天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夫仰天俯地。近身远物。莫有所遗。而风水之说。独无所取。求之十三卦。前圣之所不为者。后圣起而为之。是以。为网罟者。未暇为宫室。为舟车者。未暇为棺椁。然衣食之原。器用之利。法度之章。礼乐之则。凡民生日用之具。尚象制器者。莫不毕备于数圣人之手。韩愈氏曰。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圣人之生斯民。若是其劳且至。而风水之说。亦在所略。圣人之孝。大与达者。舜与周公也。舜之五十而慕也。未闻葬瞽瞍之如何。其生也以天下养。其死也必以天下葬矣。周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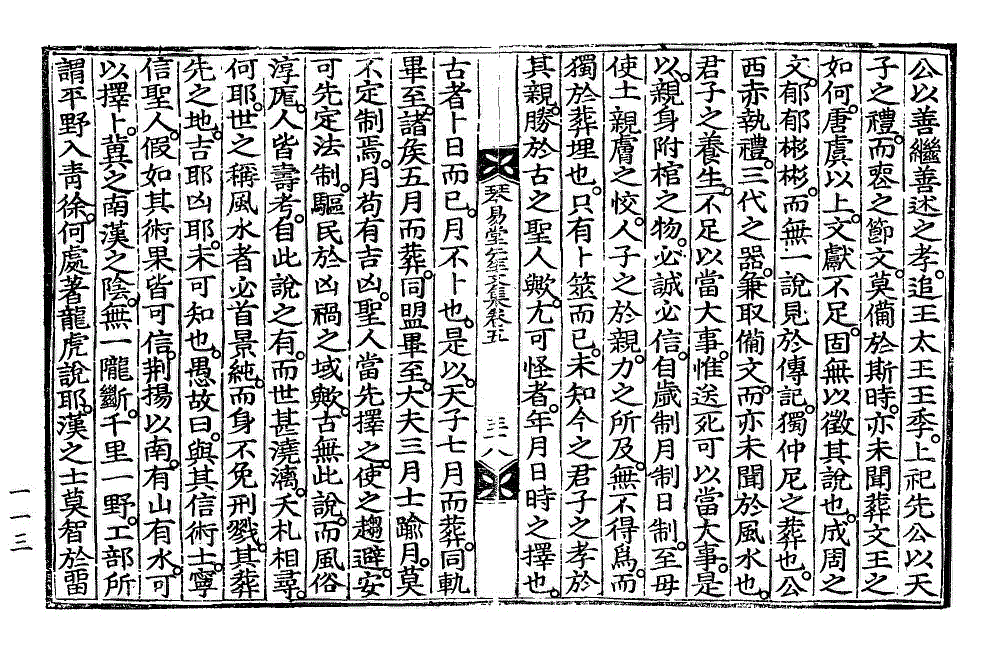 公以善继善述之孝。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而丧之节文。莫备于斯时。亦未闻葬文王之如何。唐虞以上。文献不足。固无以徵其说也。成周之文。郁郁彬彬。而无一说见于传记。独仲尼之葬也。公西赤执礼。三代之器。兼取备文。而亦未闻于风水也。君子之养生。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是以。亲身附棺之物。必诚必信。自岁制月制日制。至毋使土亲肤之恔。人子之于亲。力之所及。无不得为。而独于葬埋也。只有卜筮而已。未知今之君子之孝于其亲。胜于古之圣人欤。尤可怪者。年月日时之择也。古者卜日而已。月不卜也。是以。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而葬。同盟毕至。大夫三月士踰月。莫不定制焉。月苟有吉凶。圣人当先择之。使之趋避。安可先定法制。驱民于凶祸之域欤。古无此说。而风俗淳厖。人皆寿考。自此说之有。而世甚浇漓。夭札相寻。何耶。世之称风水者必首景纯。而身不免刑戮。其葬先之地。吉耶凶耶。未可知也。愚故曰。与其信术士。宁信圣人。假如其术果皆可信。荆扬以南。有山有水。可以择卜。冀之南汉之阴。无一陇断。千里一野。工部所谓平野入青徐。何处著龙虎说耶。汉之士莫智于留
公以善继善述之孝。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而丧之节文。莫备于斯时。亦未闻葬文王之如何。唐虞以上。文献不足。固无以徵其说也。成周之文。郁郁彬彬。而无一说见于传记。独仲尼之葬也。公西赤执礼。三代之器。兼取备文。而亦未闻于风水也。君子之养生。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是以。亲身附棺之物。必诚必信。自岁制月制日制。至毋使土亲肤之恔。人子之于亲。力之所及。无不得为。而独于葬埋也。只有卜筮而已。未知今之君子之孝于其亲。胜于古之圣人欤。尤可怪者。年月日时之择也。古者卜日而已。月不卜也。是以。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而葬。同盟毕至。大夫三月士踰月。莫不定制焉。月苟有吉凶。圣人当先择之。使之趋避。安可先定法制。驱民于凶祸之域欤。古无此说。而风俗淳厖。人皆寿考。自此说之有。而世甚浇漓。夭札相寻。何耶。世之称风水者必首景纯。而身不免刑戮。其葬先之地。吉耶凶耶。未可知也。愚故曰。与其信术士。宁信圣人。假如其术果皆可信。荆扬以南。有山有水。可以择卜。冀之南汉之阴。无一陇断。千里一野。工部所谓平野入青徐。何处著龙虎说耶。汉之士莫智于留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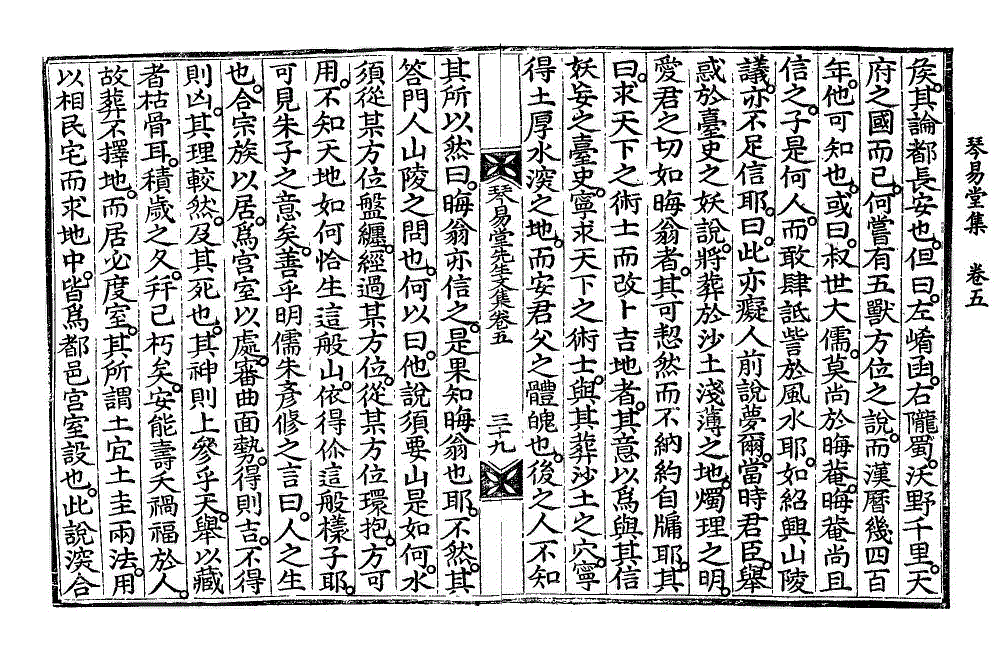 侯。其论都长安也。但曰。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天府之国而已。何尝有五兽方位之说。而汉历几四百年。他可知也。或曰。叔世大儒。莫尚于晦庵。晦庵尚且信之。子是何人。而敢肆诋訾于风水耶。如绍兴山陵议。亦不足信耶。曰。此亦痴人前说梦尔。当时君臣。举惑于台史之妖说。将葬于沙土浅薄之地。烛理之明。爱君之切如晦翁者。其可恝然而不纳约自牖耶。其曰。求天下之术士而改卜吉地者。其意以为与其信妖妄之台史。宁求天下之术士。与其葬沙土之穴。宁得土厚水深之地。而安君父之体魄也。后之人不知其所以然曰。晦翁亦信之。是果知晦翁也耶。不然。其答门人山陵之问也。何以曰。他说须要山是如何。水须从某方位盘缠。经过某方位。从某方位环抱。方可用。不知天地如何恰生这般山。依得你这般样子耶。可见朱子之意矣。善乎明儒朱彦修之言曰。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为宫室以处。审曲面势。得则吉。不得则凶。其理较然。及其死也。其神则上参乎天。举以藏者枯骨耳。积岁之久。并已朽矣。安能寿夭祸福于人。故葬不择地。而居必度室。其所谓土宜土圭两法。用以相民宅而求地中。皆为都邑宫室设也。此说深合
侯。其论都长安也。但曰。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天府之国而已。何尝有五兽方位之说。而汉历几四百年。他可知也。或曰。叔世大儒。莫尚于晦庵。晦庵尚且信之。子是何人。而敢肆诋訾于风水耶。如绍兴山陵议。亦不足信耶。曰。此亦痴人前说梦尔。当时君臣。举惑于台史之妖说。将葬于沙土浅薄之地。烛理之明。爱君之切如晦翁者。其可恝然而不纳约自牖耶。其曰。求天下之术士而改卜吉地者。其意以为与其信妖妄之台史。宁求天下之术士。与其葬沙土之穴。宁得土厚水深之地。而安君父之体魄也。后之人不知其所以然曰。晦翁亦信之。是果知晦翁也耶。不然。其答门人山陵之问也。何以曰。他说须要山是如何。水须从某方位盘缠。经过某方位。从某方位环抱。方可用。不知天地如何恰生这般山。依得你这般样子耶。可见朱子之意矣。善乎明儒朱彦修之言曰。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为宫室以处。审曲面势。得则吉。不得则凶。其理较然。及其死也。其神则上参乎天。举以藏者枯骨耳。积岁之久。并已朽矣。安能寿夭祸福于人。故葬不择地。而居必度室。其所谓土宜土圭两法。用以相民宅而求地中。皆为都邑宫室设也。此说深合琴易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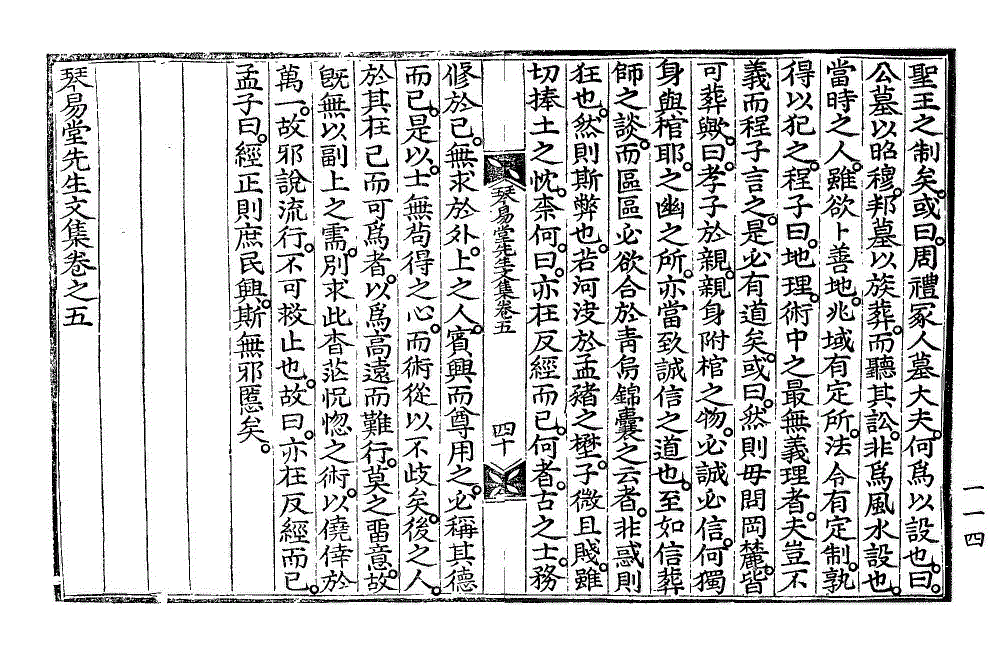 圣王之制矣。或曰。周礼冢人墓大夫。何为以设也。曰。公墓以昭穆。邦墓以族葬。而听其讼。非为风水设也。当时之人。虽欲卜善地。兆域有定所。法令有定制。孰得以犯之。程子曰。地理。术中之最无义理者。夫岂不义而程子言之。是必有道矣。或曰。然则毋问冈麓。皆可葬欤。曰。孝子于亲。亲身附棺之物。必诚必信。何独身与棺耶。之幽之所。亦当致诚信之道也。至如信葬师之谈。而区区必欲合于青乌锦囊之云者。非惑则狂也。然则斯弊也。若河决于孟猪之壄。子微且贱。虽切捧土之忱。奈何。曰。亦在反经而已。何者。古之士。务修于己。无求于外。上之人。宾兴而尊用之。必称其德而已。是以。士无苟得之心。而术从以不岐矣。后之人。于其在己而可为者。以为高远而难行。莫之留意。故既无以副上之需。别求此杳茫恍惚之术。以侥倖于万一。故邪说流行。不可救止也。故曰。亦在反经而已。孟子曰。经正则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圣王之制矣。或曰。周礼冢人墓大夫。何为以设也。曰。公墓以昭穆。邦墓以族葬。而听其讼。非为风水设也。当时之人。虽欲卜善地。兆域有定所。法令有定制。孰得以犯之。程子曰。地理。术中之最无义理者。夫岂不义而程子言之。是必有道矣。或曰。然则毋问冈麓。皆可葬欤。曰。孝子于亲。亲身附棺之物。必诚必信。何独身与棺耶。之幽之所。亦当致诚信之道也。至如信葬师之谈。而区区必欲合于青乌锦囊之云者。非惑则狂也。然则斯弊也。若河决于孟猪之壄。子微且贱。虽切捧土之忱。奈何。曰。亦在反经而已。何者。古之士。务修于己。无求于外。上之人。宾兴而尊用之。必称其德而已。是以。士无苟得之心。而术从以不岐矣。后之人。于其在己而可为者。以为高远而难行。莫之留意。故既无以副上之需。别求此杳茫恍惚之术。以侥倖于万一。故邪说流行。不可救止也。故曰。亦在反经而已。孟子曰。经正则庶民兴。斯无邪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