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x 页
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疏
疏
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11H 页
 辞掌令疏(癸亥三月)
辞掌令疏(癸亥三月)伏以国运不幸。奸臣秉柄。怂恿君上。㭬丧邦命。彝伦斁败。民生涂炭。 宗社岌岌。朝夕将亡。幸赖皇天眷佑我东。聿生 大圣。以至今日。拨乱反正。 慈圣复位。黎庶奠枕。此殆 宗社亿万斯年之庆也。方当代暴以仁。釐正庶务。日不暇给之际。首 下隆旨。召臣以掌宪之职。臣承 命惊皇。措躬无地。臣本京华世族。生长宰枢之家。荫仕平进三十馀年。官至三品。本非山林高蹈。有离群遁世之志者也。万历癸丑。惨遭家祸。幸免屠灭。蛰伏田庐。为一编氓。岂料当此改纪之日。首膺 明命乎。目今 圣上旁招。群彦汇征。可谓千载一时。臣苟有一分材具可以仰补 新化者。则何敢暂俟驾屦而进哉。臣内自循省。无所肖似。而加以年纪衰迟。筋力耗倦。寻常起居。亦且须人。虽欲扶曳就道。其路末由。况且以此癃疾。匍匐道路。则岂不大骇瞻视。以为 圣世之丑累哉。玆不敢冒承 恩命。伏乞 圣明亟递臣职。俾安微分。千万幸甚。臣无任瞻天望 圣激切屏营之至。谨昧死以 闻。
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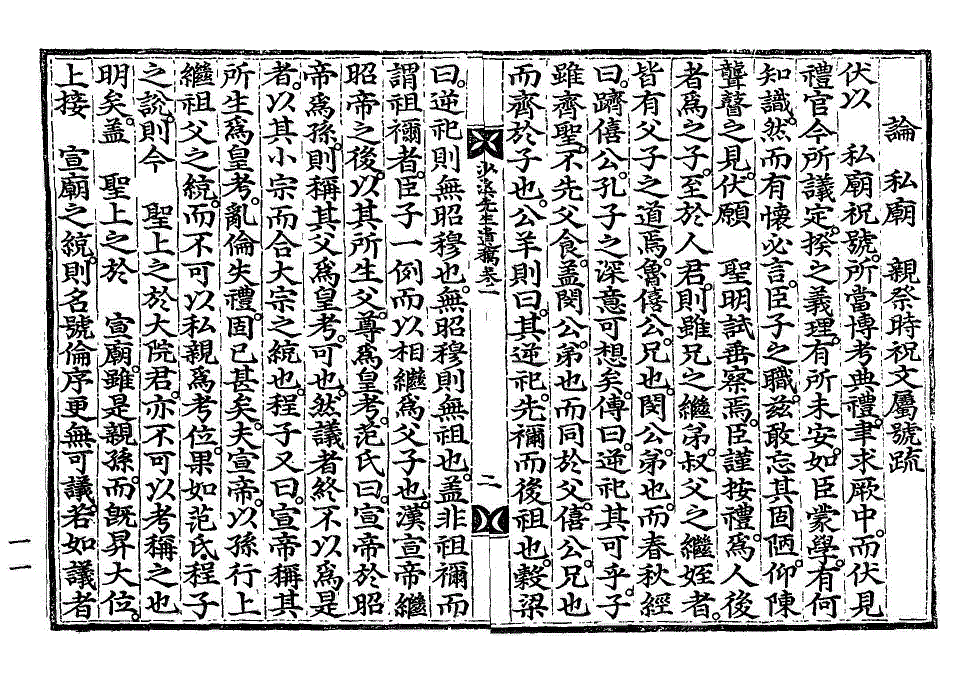 论 私庙 亲祭时祝文属号疏
论 私庙 亲祭时祝文属号疏伏以 私庙祝号。所当博考典礼。聿求厥中。而伏见礼官今所议定。揆之义理。有所未安。如臣蒙学。有何知识。然而有怀必言。臣子之职。玆敢忘其固陋。仰陈聋瞽之见。伏愿 圣明试垂察焉。臣谨按礼。为人后者为之子。至于人君。则虽兄之继弟。叔父之继侄者。皆有父子之道焉。鲁僖公。兄也。闵公。弟也。而春秋经曰。跻僖公。孔子之深意可想矣。传曰。逆祀其可乎。子虽齐圣。不先父食。盖闵公。弟也而同于父。僖公。兄也而齐于子也。公羊则曰。其逆祀。先祢而后祖也。榖粱曰。逆祀则无昭穆也。无昭穆则无祖也。盖非祖祢而谓祖祢者。臣子一例而以相继为父子也。汉宣帝继昭帝之后。以其所生父。尊为皇考。范氏曰。宣帝于昭帝为孙。则称其父为皇考。可也。然议者终不以为是者。以其小宗而合大宗之统也。程子又曰。宣帝称其所生为皇考。乱伦失礼。固已甚矣。夫宣帝。以孙行上继祖父之统。而不可以私亲为考位。果如范氏,程子之说。则今 圣上之于大院君。亦不可以考称之也明矣。盖 圣上之于 宣庙。虽是亲孙。而既升大位。上接 宣庙之统。则名号伦序更无可议。若如议者
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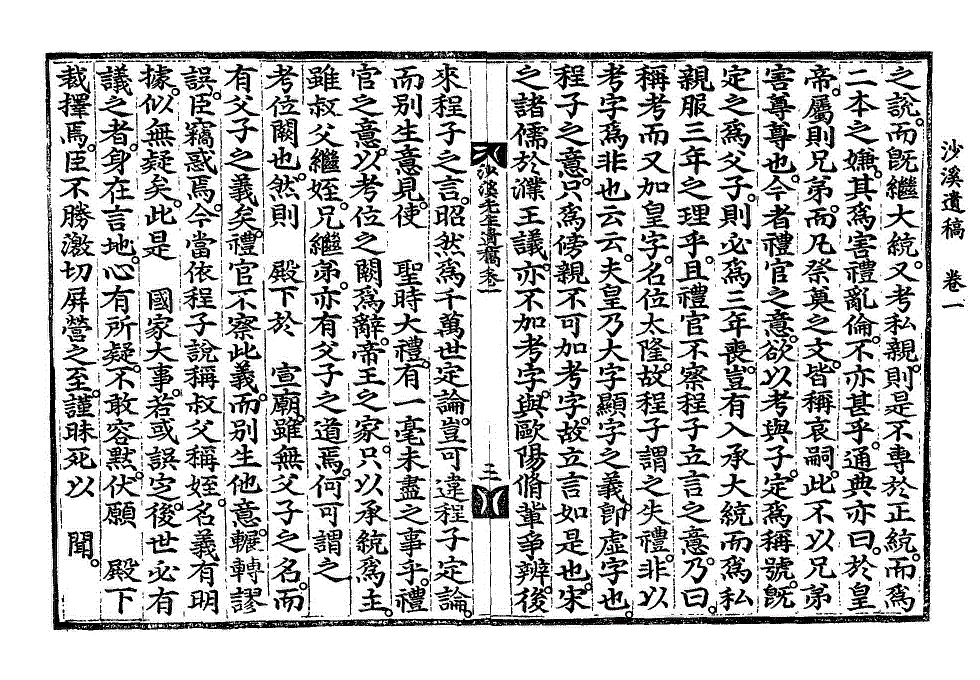 之说。而既继大统。又考私亲。则是不专于正统。而为二本之嫌。其为害礼乱伦。不亦甚乎。通典亦曰。于皇帝。属则兄弟。而凡祭奠之文。皆称哀嗣。此不以兄弟害尊尊也。今者礼官之意。欲以考与子。定为称号。既定之为父子。则必为三年丧。岂有入承大统而为私亲服三年之理乎。且礼官不察程子立言之意。乃曰。称考而又加皇字。名位太隆。故程子谓之失礼。非以考字为非也云云。夫皇乃大字显字之义。即虚字也。程子之意。只为傍亲不可加考字。故立言如是也。宋之诸儒于濮王议。亦不加考字。与欧阳脩辈争辨。后来程子之言。昭然为千万世定论。岂可违程子定论。而别生意见。使 圣时大礼。有一毫未尽之事乎。礼官之意。以考位之阙为辞。帝王之家。只以承统为主。虽叔父继侄。兄继弟。亦有父子之道焉。何可谓之 考位阙也。然则 殿下于 宣庙。虽无父子之名。而有父子之义矣。礼官不察此义。而别生他意。辗转谬误。臣窃惑焉。今当依程子说称叔父称侄。名义有明据。似无疑矣。此是 国家大事。若或误定。后世必有议之者。身在言地。心有所疑。不敢容默。伏愿 殿下裁择焉。臣不胜激切屏营之至。谨昧死以 闻。
之说。而既继大统。又考私亲。则是不专于正统。而为二本之嫌。其为害礼乱伦。不亦甚乎。通典亦曰。于皇帝。属则兄弟。而凡祭奠之文。皆称哀嗣。此不以兄弟害尊尊也。今者礼官之意。欲以考与子。定为称号。既定之为父子。则必为三年丧。岂有入承大统而为私亲服三年之理乎。且礼官不察程子立言之意。乃曰。称考而又加皇字。名位太隆。故程子谓之失礼。非以考字为非也云云。夫皇乃大字显字之义。即虚字也。程子之意。只为傍亲不可加考字。故立言如是也。宋之诸儒于濮王议。亦不加考字。与欧阳脩辈争辨。后来程子之言。昭然为千万世定论。岂可违程子定论。而别生意见。使 圣时大礼。有一毫未尽之事乎。礼官之意。以考位之阙为辞。帝王之家。只以承统为主。虽叔父继侄。兄继弟。亦有父子之道焉。何可谓之 考位阙也。然则 殿下于 宣庙。虽无父子之名。而有父子之义矣。礼官不察此义。而别生他意。辗转谬误。臣窃惑焉。今当依程子说称叔父称侄。名义有明据。似无疑矣。此是 国家大事。若或误定。后世必有议之者。身在言地。心有所疑。不敢容默。伏愿 殿下裁择焉。臣不胜激切屏营之至。谨昧死以 闻。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12L 页
 (谨按。当时论议多歧。大抵皆异于先生。先生之意则以为周平王太子之子桓王林。不追崇其考。是以孙继祖也。汉宣帝之于昭帝。虽是从孙。以昭穆言之。则祖孙之名犹在。而追尊其父则程子以为乱伦。光武实同创业。而立四亲庙于洛阳。朱子以立伯升之子。以奉私庙。为最得。故先生之论。终始主此数说。详见典礼全书。)
(谨按。当时论议多歧。大抵皆异于先生。先生之意则以为周平王太子之子桓王林。不追崇其考。是以孙继祖也。汉宣帝之于昭帝。虽是从孙。以昭穆言之。则祖孙之名犹在。而追尊其父则程子以为乱伦。光武实同创业。而立四亲庙于洛阳。朱子以立伯升之子。以奉私庙。为最得。故先生之论。终始主此数说。详见典礼全书。)辞 元子僚属成均司业疏(癸亥六月)
伏以臣以年老身病。解职调理。未几又差成均司业。久未出谢。至为未安。故昨日将欲肃拜。已呈单字。而臣猝患霍乱。终不得诣 阙。臣不胜惶恐待罪。仍念臣赋性鲁钝。百事不能如人。虽尝从师问学。而所习不出句读训诰之间。其于明体适用之实。则了无分毫所得。加以老耄癃疾。神精昏愦。耳聋尤甚。自分为世弃物。毕命丘樊矣。不料虚名上彻。误 恩荐及。授以风宪之官。待以非常之礼。臣衔感 鸿恩。扶曳赴召。居官数月。尸素餔啜。曾无报效。而 恩礼有加。至于吃着所须。皆蒙 轸念。诚非昏耄微臣所敢当也。解官之后。便欲乞 赐骸骨。归死田里。而 圣明在上。不忍告诀。迟回旅舍。苟延时月。今者官僚国子之命。一时并下。臣诚忧惶惭恧。不知所以自处也。臣闻。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如或掇拾口耳。自无实得。则其何能有以及人哉。如臣愚陋。自知甚明。虽后生小
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13H 页
 子时有问业者。犹不敢偃然当席。况今 元子以冲年妙质。讲学方急。辅导启迪。责任至重。故师傅之官。皆极一时之选。臣名虽僚属。 元子待之拟埒师傅。臣之滥黩名器。虽不暇言。而独不念调护之失宜。劝讲之乖方乎。至如成均之职。 祖宗旧制。必用文官。意盖有在。二百年来。未之或改。虽以故儒臣成浑之硕德重望。一时大臣。犹以为难。今者为万不近似之人。开前所未有之制。人器不称。名实刺谬。况刱设官名。瞻聆尤骇。臣虽欲强颜承命。其于公议之可畏。多士之指点。何哉。今臣欲黾勉就列。则廉隅所关。不敢冒昧。欲投劾径归。则 恩眷隆重。未忍决去。进退狼狈。心事瞀乱。兼之溽暑所伤。疾病侵凌。精神筋力。日就消脱。揆分量力。都无可堪之理。伏愿 圣慈曲赐矜察。将臣宫僚及司业职名。亟 命镌改。俾朝夕将死之臣。得返丘园。以尽馀年。不胜幸甚。
子时有问业者。犹不敢偃然当席。况今 元子以冲年妙质。讲学方急。辅导启迪。责任至重。故师傅之官。皆极一时之选。臣名虽僚属。 元子待之拟埒师傅。臣之滥黩名器。虽不暇言。而独不念调护之失宜。劝讲之乖方乎。至如成均之职。 祖宗旧制。必用文官。意盖有在。二百年来。未之或改。虽以故儒臣成浑之硕德重望。一时大臣。犹以为难。今者为万不近似之人。开前所未有之制。人器不称。名实刺谬。况刱设官名。瞻聆尤骇。臣虽欲强颜承命。其于公议之可畏。多士之指点。何哉。今臣欲黾勉就列。则廉隅所关。不敢冒昧。欲投劾径归。则 恩眷隆重。未忍决去。进退狼狈。心事瞀乱。兼之溽暑所伤。疾病侵凌。精神筋力。日就消脱。揆分量力。都无可堪之理。伏愿 圣慈曲赐矜察。将臣宫僚及司业职名。亟 命镌改。俾朝夕将死之臣。得返丘园。以尽馀年。不胜幸甚。辞元子僚属成均司业疏[二](癸亥八月)
伏以臣才疏学浅。盗窃虚名。猥蒙 圣眷。取讥负乘。而犬马之齿。又近八十。揆古人致仕之年。已踰六岁。虽无疾病之婴身。精神日耗。志气日衰。加以耳聋尤甚。寻常言语。专不听闻。顷日 榻前。 天语温谆。俾
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13L 页
 尽所蕴。而 玉音屡下。或有未闻。问诸承旨。然后始得钦承。惶恐陨越。若坠深渊。卤莽之怀。亦未悉陈。退伏旅舍。只俟谴责。而又念 元子气质英明。若能辅导尽方。则大有所成。而非但微臣灭裂之学无所辅益。亦缘病聩。口读之外。无复论难。每日公退。内顾恧然。揆分量力。只合退死田野而已。 经筵入侍。讲厅僚属之任。岂是许丞但能拜起者之为哉。而怀禄贪宠。彷徨不去。已至半年之久。俯仰愧怍。若无所容。 圣度如海。含垢包荒。僭赏谬 恩。日以隆深。臣非木石。宁不感激。慈以犯羲易知进之戒。冒诗人素餐之诮。强颜趋跄。不敢告退矣。今者私心切至。不得不再渎 天威。伏愿 殿下垂察焉。臣先墓远在湖西。木主亦留乡村。仲月屡经。霜露迁变。怵惕之心。焄蒿之感。日以益切。衰朽馀生。死亡无日。常恐不得复归。写攀柏之悲。行亲涖之奠。中夜不寐。有泪盈襟。扫坟给暇。 国典所载。拟及秋夕。依例受暇。而适会 国有大谳。不敢上请。今则狱事已完。 朝廷无事。玆敢冒昧陈乞。冀伸宿愿。臣之母忌。又在开月。趁及生前。更省坟茔。仍哭丧馀。而归骨山足。永依松柏。则岂但微臣陨结图报。死者有知。亦且感泣于地下矣。臣无任
尽所蕴。而 玉音屡下。或有未闻。问诸承旨。然后始得钦承。惶恐陨越。若坠深渊。卤莽之怀。亦未悉陈。退伏旅舍。只俟谴责。而又念 元子气质英明。若能辅导尽方。则大有所成。而非但微臣灭裂之学无所辅益。亦缘病聩。口读之外。无复论难。每日公退。内顾恧然。揆分量力。只合退死田野而已。 经筵入侍。讲厅僚属之任。岂是许丞但能拜起者之为哉。而怀禄贪宠。彷徨不去。已至半年之久。俯仰愧怍。若无所容。 圣度如海。含垢包荒。僭赏谬 恩。日以隆深。臣非木石。宁不感激。慈以犯羲易知进之戒。冒诗人素餐之诮。强颜趋跄。不敢告退矣。今者私心切至。不得不再渎 天威。伏愿 殿下垂察焉。臣先墓远在湖西。木主亦留乡村。仲月屡经。霜露迁变。怵惕之心。焄蒿之感。日以益切。衰朽馀生。死亡无日。常恐不得复归。写攀柏之悲。行亲涖之奠。中夜不寐。有泪盈襟。扫坟给暇。 国典所载。拟及秋夕。依例受暇。而适会 国有大谳。不敢上请。今则狱事已完。 朝廷无事。玆敢冒昧陈乞。冀伸宿愿。臣之母忌。又在开月。趁及生前。更省坟茔。仍哭丧馀。而归骨山足。永依松柏。则岂但微臣陨结图报。死者有知。亦且感泣于地下矣。臣无任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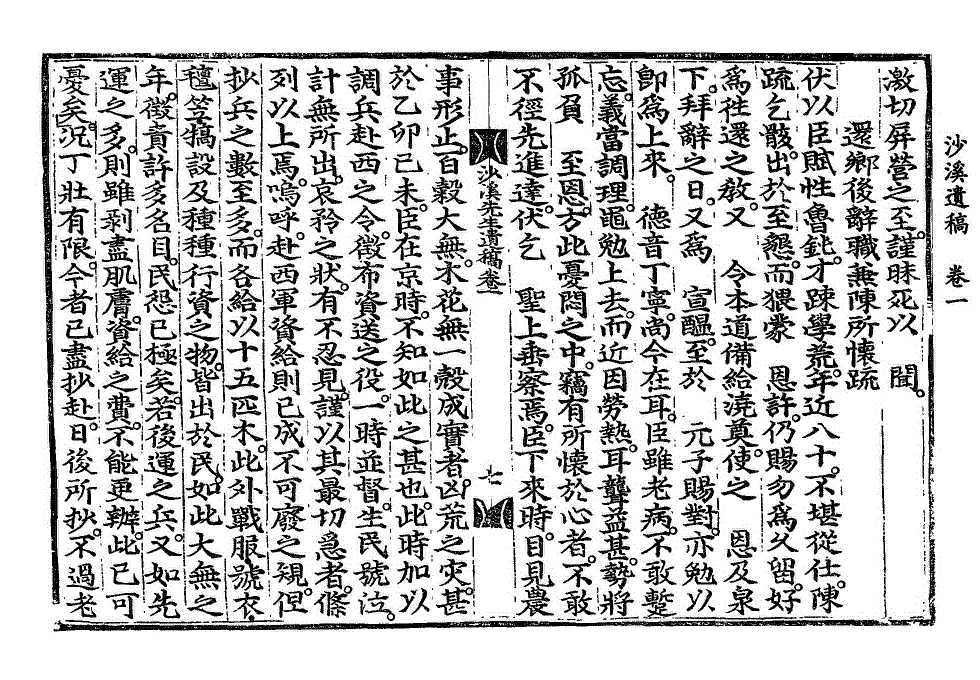 激切屏营之至。谨昧死以 闻。
激切屏营之至。谨昧死以 闻。还乡后辞职兼陈所怀疏
伏以臣赋性鲁钝。才疏学荒。年近八十。不堪从仕。陈疏乞骸。出于至恳。而猥蒙 恩许。仍赐勿为久留。好为往还之教。又 令本道备给浇奠。使之 恩及泉下。拜辞之日。又为 宣酝。至于 元子赐对。亦勉以即为上来。 德音丁宁。尚今在耳。臣虽老病。不敢暂忘。义当调理。黾勉上去。而近因劳热。耳聋益甚。势将孤负 至恩。方此忧闷之中。窃有所怀于心者。不敢不径先进达。伏乞 圣上垂察焉。臣下来时。目见农事形止。百谷大无。木花无一壳成实者。凶荒之灾。甚于乙卯己未。臣在京时。不知如此之甚也。此时加以调兵赴西之令。徵布资送之役。一时并督。生民号泣。计无所出。哀矜之状。有不忍见。谨以其最切急者。条列以上焉。呜呼。赴西军资给则已成不可废之规。但抄兵之数至多。而各给以十五匹木。此外战服,号衣,毡笠,犒设及种种行资之物。皆出于民。如此大无之年。徵责许多名目。民怨已极矣。若后运之兵。又如先运之多。则虽剥尽肌肤。资给之费。不能更办。此已可忧矣。况丁壮有限。今者已尽抄赴。日后所抄。不过老
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14L 页
 残无用之兵。而又徵资送之布则臣恐无补于御敌。而内溃之祸先至也。兵志曰。兵务精不务多。臣愿亟令兵曹。精选而减其数。一以除西边馈饷之烦。一以纾内民资送之苦焉。夫以两湖赴西之军。多至七千。而同时发送。刻日登道。资装粮刍。皆令及期。监司催督于列邑。列邑催督于民间。哀此困悴之民。其何以得办于期会之内哉。虽山积而鬼输。且犹不及。况此赤立之馀乎。今计莫若先后分运。以纾发送之期。则其装其犒。次次周旋。民可以容其力。官可以行其令。而于军政。亦无所害矣。且今收布之规。因用辛酉田结之数。此尤招怨之大者也。盖随其时。起实数而税敛于民者。乃 国家经乱后便民之政也。向在废朝。择其稍穰之岁田结最多之数。以为多取之计。而严立事目。故敬差官承风于覆审之际。勒定自觉。鞭笞狼藉。守令不敢从其实。下吏只欲免其罪。至于虚张若是其多也。以今时起之实。准之于辛酉之数。则未满三分之二焉。而所收之布。一依辛酉年例。则臣恐往时多取之弊。未见革于 新化。而当初 德音。不见信于民也。忠清道则今因监司申鉴状 启。蠲减逐结收布之令。民皆欢欣鼓舞。臣以为通八道一体
残无用之兵。而又徵资送之布则臣恐无补于御敌。而内溃之祸先至也。兵志曰。兵务精不务多。臣愿亟令兵曹。精选而减其数。一以除西边馈饷之烦。一以纾内民资送之苦焉。夫以两湖赴西之军。多至七千。而同时发送。刻日登道。资装粮刍。皆令及期。监司催督于列邑。列邑催督于民间。哀此困悴之民。其何以得办于期会之内哉。虽山积而鬼输。且犹不及。况此赤立之馀乎。今计莫若先后分运。以纾发送之期。则其装其犒。次次周旋。民可以容其力。官可以行其令。而于军政。亦无所害矣。且今收布之规。因用辛酉田结之数。此尤招怨之大者也。盖随其时。起实数而税敛于民者。乃 国家经乱后便民之政也。向在废朝。择其稍穰之岁田结最多之数。以为多取之计。而严立事目。故敬差官承风于覆审之际。勒定自觉。鞭笞狼藉。守令不敢从其实。下吏只欲免其罪。至于虚张若是其多也。以今时起之实。准之于辛酉之数。则未满三分之二焉。而所收之布。一依辛酉年例。则臣恐往时多取之弊。未见革于 新化。而当初 德音。不见信于民也。忠清道则今因监司申鉴状 启。蠲减逐结收布之令。民皆欢欣鼓舞。臣以为通八道一体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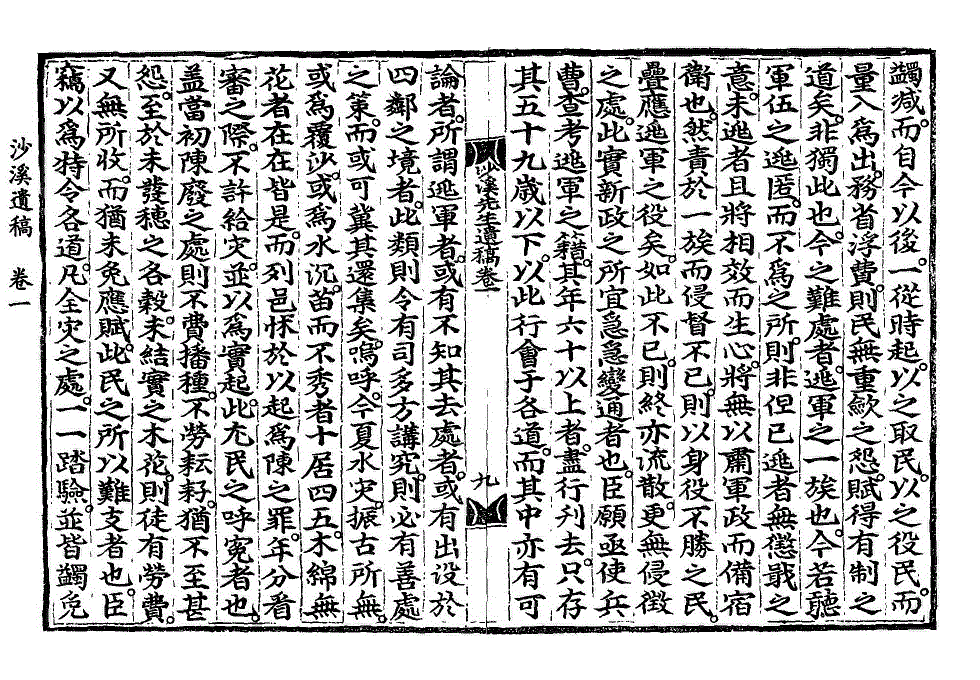 蠲减。而自今以后。一从时起。以之取民。以之役民。而量入为出。务省浮费。则民无重敛之怨。赋得有制之道矣。非独此也。今之难处者。逃军之一族也。今若听军伍之逃匿。而不为之所。则非但已逃者无惩戢之意。未逃者且将相效而生心。将无以肃军政而备宿卫也。然责于一族而侵督不已。则以身役不胜之民。叠应逃军之役矣。如此不已。则终亦流散。更无侵徵之处。此实新政之所宜急急变通者也。臣愿亟使兵曹。查考逃军之籍。其年六十以上者。尽行刋去。只存其五十九岁以下。以此行会于各道。而其中亦有可论者。所谓逃军者。或有不知其去处者。或有出没于四邻之境者。此类则令有司多方讲究。则必有善处之策。而或可冀其还集矣。呜呼。今夏水灾。振古所无。或为覆沙。或为水沈。苗而不秀者十居四五。木绵无花者在在皆是。而列邑怵于以起为陈之罪。年分看审之际。不许给灾。并以为实起。此尤民之呼冤者也。盖当初陈废之处则不费播种。不劳耘耔。犹不至甚怨。至于未发穗之各谷。未结实之木花。则徒有劳费。又无所收。而犹未免应赋。此民之所以难支者也。臣窃以为特令各道。凡全灾之处。一一踏验。并皆蠲免
蠲减。而自今以后。一从时起。以之取民。以之役民。而量入为出。务省浮费。则民无重敛之怨。赋得有制之道矣。非独此也。今之难处者。逃军之一族也。今若听军伍之逃匿。而不为之所。则非但已逃者无惩戢之意。未逃者且将相效而生心。将无以肃军政而备宿卫也。然责于一族而侵督不已。则以身役不胜之民。叠应逃军之役矣。如此不已。则终亦流散。更无侵徵之处。此实新政之所宜急急变通者也。臣愿亟使兵曹。查考逃军之籍。其年六十以上者。尽行刋去。只存其五十九岁以下。以此行会于各道。而其中亦有可论者。所谓逃军者。或有不知其去处者。或有出没于四邻之境者。此类则令有司多方讲究。则必有善处之策。而或可冀其还集矣。呜呼。今夏水灾。振古所无。或为覆沙。或为水沈。苗而不秀者十居四五。木绵无花者在在皆是。而列邑怵于以起为陈之罪。年分看审之际。不许给灾。并以为实起。此尤民之呼冤者也。盖当初陈废之处则不费播种。不劳耘耔。犹不至甚怨。至于未发穗之各谷。未结实之木花。则徒有劳费。又无所收。而犹未免应赋。此民之所以难支者也。臣窃以为特令各道。凡全灾之处。一一踏验。并皆蠲免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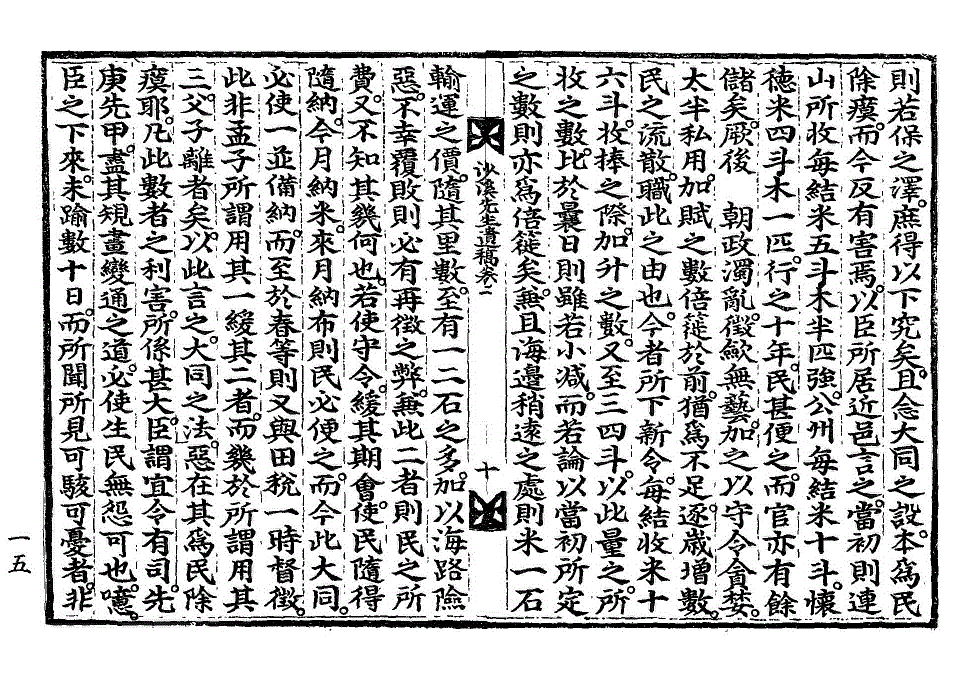 则若保之泽。庶得以下究矣。且念大同之设。本为民除瘼。而今反有害焉。以臣所居近邑言之。当初则连山所收每结米五斗,木半匹强。公州每结米十斗。怀德米四斗,木一匹。行之十年。民甚便之。而官亦有馀储矣。厥后 朝政浊乱。徵敛无艺。加之以守令贪婪。太半私用。加赋之数倍蓰于前。犹为不足。逐岁增数。民之流散。职此之由也。今者所下新令。每结收米十六斗。收捧之际。加升之数。又至三四斗。以此量之。所收之数。比于曩日则虽若小减。而若论以当初所定之数则亦为倍蓰矣。兼且海边稍远之处则米一石输运之价。随其里数。至有一二石之多。加以海路险恶。不幸覆败则必有再徵之弊。兼此二者则民之所费。又不知其几何也。若使守令。缓其期会。使民随得随纳。今月纳米。来月纳布则民必便之。而今此大同。必使一并备纳。而至于春等则又与田税一时督徵。此非孟子所谓用其一缓其二者。而几于所谓用其三。父子离者矣。以此言之。大同之法。恶在其为民除瘼耶。凡此数者之利害。所系甚大。臣谓宜令有司。先庚先甲。尽其规画变痛之道。必使生民无怨可也。噫。臣之下来。未踰数十日。而所闻所见可骇可忧者。非
则若保之泽。庶得以下究矣。且念大同之设。本为民除瘼。而今反有害焉。以臣所居近邑言之。当初则连山所收每结米五斗,木半匹强。公州每结米十斗。怀德米四斗,木一匹。行之十年。民甚便之。而官亦有馀储矣。厥后 朝政浊乱。徵敛无艺。加之以守令贪婪。太半私用。加赋之数倍蓰于前。犹为不足。逐岁增数。民之流散。职此之由也。今者所下新令。每结收米十六斗。收捧之际。加升之数。又至三四斗。以此量之。所收之数。比于曩日则虽若小减。而若论以当初所定之数则亦为倍蓰矣。兼且海边稍远之处则米一石输运之价。随其里数。至有一二石之多。加以海路险恶。不幸覆败则必有再徵之弊。兼此二者则民之所费。又不知其几何也。若使守令。缓其期会。使民随得随纳。今月纳米。来月纳布则民必便之。而今此大同。必使一并备纳。而至于春等则又与田税一时督徵。此非孟子所谓用其一缓其二者。而几于所谓用其三。父子离者矣。以此言之。大同之法。恶在其为民除瘼耶。凡此数者之利害。所系甚大。臣谓宜令有司。先庚先甲。尽其规画变痛之道。必使生民无怨可也。噫。臣之下来。未踰数十日。而所闻所见可骇可忧者。非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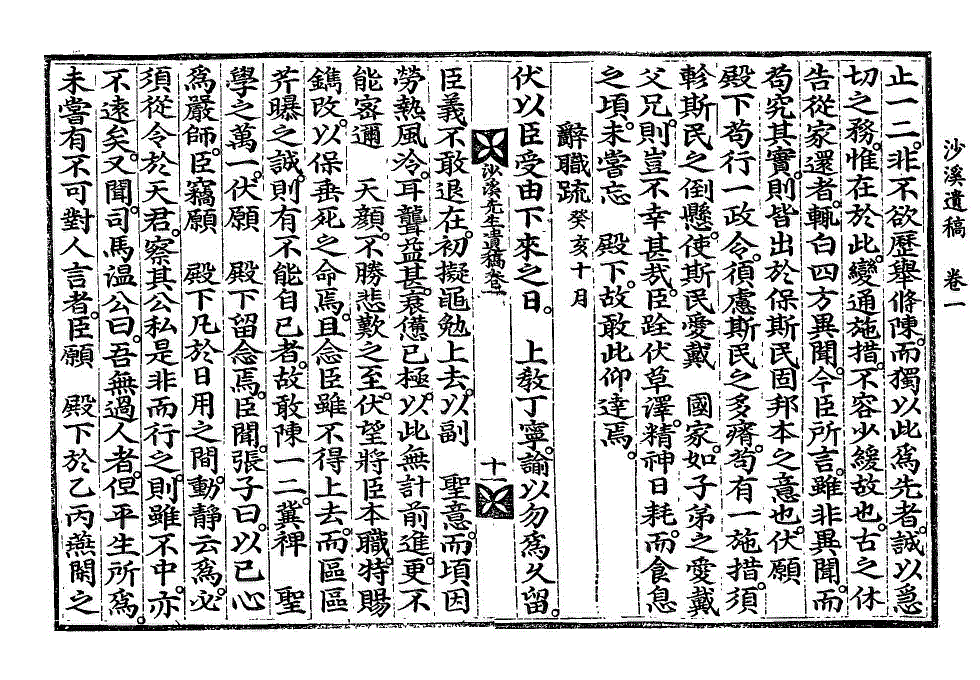 止一二。非不欲历举条陈。而独以此为先者。诚以急切之务。惟在于此。变通施措。不容少缓故也。古之休告从家还者。辄白四方异闻。今臣所言。虽非异闻。而苟究其实。则皆出于保斯民固邦本之意也。伏愿 殿下苟行一政令。须虑斯民之多瘠。苟有一施措。须轸斯民之倒悬。使斯民爱戴 国家。如子弟之爱戴父兄。则岂不幸甚哉。臣跧伏草泽。精神日耗。而食息之顷。未尝忘 殿下。故敢此仰达焉。
止一二。非不欲历举条陈。而独以此为先者。诚以急切之务。惟在于此。变通施措。不容少缓故也。古之休告从家还者。辄白四方异闻。今臣所言。虽非异闻。而苟究其实。则皆出于保斯民固邦本之意也。伏愿 殿下苟行一政令。须虑斯民之多瘠。苟有一施措。须轸斯民之倒悬。使斯民爱戴 国家。如子弟之爱戴父兄。则岂不幸甚哉。臣跧伏草泽。精神日耗。而食息之顷。未尝忘 殿下。故敢此仰达焉。辞职疏(癸亥十月)
伏以臣受由下来之日。 上教丁宁。谕以勿为久留。臣义不敢退在。初拟黾勉上去。以副 圣意。而顷因劳热风冷。耳聋益甚。衰惫已极。以此无计前进。更不能密迩 天颜。不胜悲叹之至。伏望将臣本职。特赐镌改。以保垂死之命焉。且念臣虽不得上去。而区区芹曝之诚。则有不能自已者。故敢陈一二。冀裨 圣学之万一。伏愿 殿下留念焉。臣闻。张子曰。以己心为严帅。臣窃愿 殿下凡于日用之间。动静云为。必须从令于天君。察其公私是非而行之。则虽不中。亦不远矣。又闻。司马温公曰。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臣愿殿下于乙丙燕闲之
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16L 页
 时。幽独得肆之地。一念之微。一事之细。皆存诚敬。无愧于屋漏。则虽对群臣。无有所隐。而心身安舒洞彻矣。臣自少以此二说。常常服膺。而不能践行。今者敢以为献 殿下傥能用力于此则大有益于 圣学。而 国家幸甚。臣民幸甚。臣无任激切祈望之至。
时。幽独得肆之地。一念之微。一事之细。皆存诚敬。无愧于屋漏。则虽对群臣。无有所隐。而心身安舒洞彻矣。臣自少以此二说。常常服膺。而不能践行。今者敢以为献 殿下傥能用力于此则大有益于 圣学。而 国家幸甚。臣民幸甚。臣无任激切祈望之至。辞职疏[二](癸亥十月)
伏以小臣。生长世族之家。筮仕 宣庙朝三十馀年。位至三品。至癸丑。以庶弟被罪之故。虽并废弃。而本非不欲仕也。亦非有山林避世之志者也。及至 圣明即位之初。起于久废之中。擢为台宪之官。又令出入 经筵。教诲 元子。臣之荣幸极矣。又无可去之义矣。只缘老病重听。又值冬月。则寒疾辄发。以故。久未上去。以负 圣恩。臣罪大矣。不料 殿下曲赐财赦。而且勤记念。屡下 召命。辞旨恳恻。不胜感激惶恐之至。第臣癃疾。终有所难强者。而下来数月。尚带职名。伏乞亟赐递免。以安愚分。无任激切屏营之至。
甲子适变时待罪疏(甲子二月)
伏以臣去冬。祗承 圣旨。许以开春上来。以臣犬马之贱。而 圣上所以轸念眷待者如此其至。臣感荷隆恩。日夜陨越而已。不意玆者。贼臣称兵。罪恶滔天。
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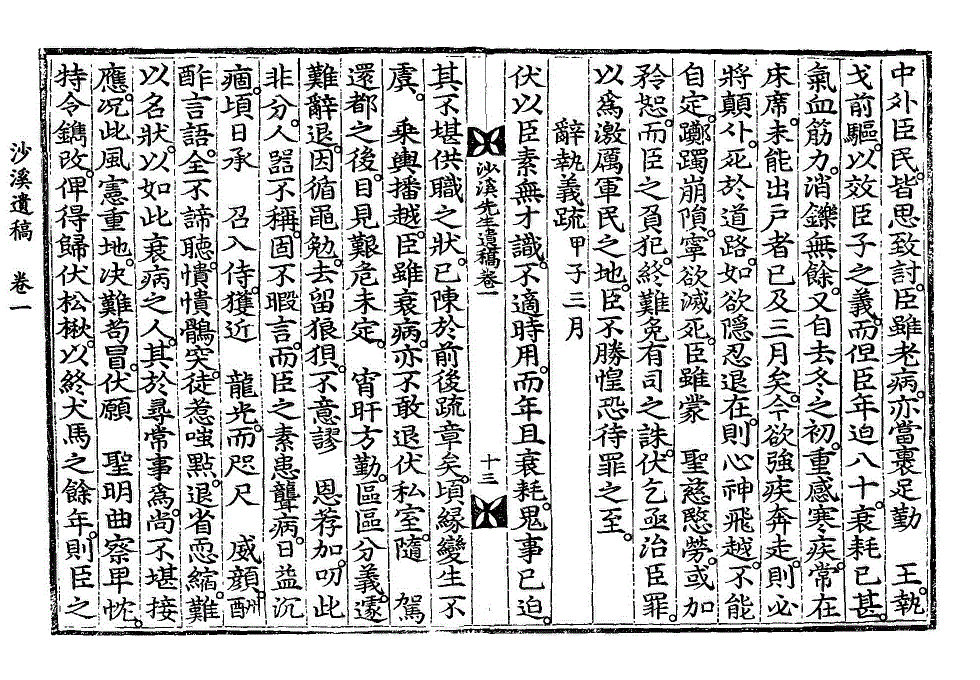 中外臣民。皆思致讨。臣虽老病。亦当裹足勤 王。执戈前驱。以效臣子之义。而但臣年迫八十。衰耗已甚。气血筋力。消铄无馀。又自去冬之初。重感寒疾。常在床席。未能出户者已及三月矣。今欲强疾奔走。则必将颠仆。死于道路。如欲隐忍退在。则心神飞越。不能自定。踯躅崩陨。宁欲灭死。臣虽蒙 圣慈悯劳。或加矜恕。而臣之负犯。终难免有司之诛。伏乞亟治臣罪。以为激厉军民之地。臣不胜惶恐待罪之至。
中外臣民。皆思致讨。臣虽老病。亦当裹足勤 王。执戈前驱。以效臣子之义。而但臣年迫八十。衰耗已甚。气血筋力。消铄无馀。又自去冬之初。重感寒疾。常在床席。未能出户者已及三月矣。今欲强疾奔走。则必将颠仆。死于道路。如欲隐忍退在。则心神飞越。不能自定。踯躅崩陨。宁欲灭死。臣虽蒙 圣慈悯劳。或加矜恕。而臣之负犯。终难免有司之诛。伏乞亟治臣罪。以为激厉军民之地。臣不胜惶恐待罪之至。辞执义疏(甲子三月)
伏以臣素无才识。不适时用。而年且衰耗。鬼事已迫。其不堪供职之状。已陈于前后疏章矣。顷缘变生不虞。 乘舆播越。臣虽衰病。亦不敢退伏私室。随 驾还都之后。目见艰危未定。 宵旰方勤。区区分义。遽难辞退。因循黾勉。去留狼狈。不意谬 恩荐加。叨此非分。人器不称。固不暇言。而臣之素患聋疾。日益沈痼。顷日承 召入侍。获近 龙光。而咫尺 威颜。酬酢言语。全不谛听。愦愦鹘突。徒惹嗤点。退省恧缩。难以名状。以如此衰病之人。其于寻常事为。尚不堪接应。况此风宪重地。决难苟冒。伏愿 圣明曲察卑忱。特令镌改。俾得归伏松楸。以终犬马之馀年。则臣之
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17L 页
 死生。皆是天地生成之德也。臣无任兢惶危迫之至。
死生。皆是天地生成之德也。臣无任兢惶危迫之至。辞执义疏[二](甲子五月)
伏以臣猥蒙 恩命。许省丘垄。既蒙 给暇。且 赐浇奠。暨至拜辞之日。 宣以内酝。副以腊剂。误 恩异数。感极幽明。非臣陨结所能图报。唯当扫除墓道讫。旋即趋还。以谢 洪私。而残骸老喘。重伤炎路。委顿床席。无路起动。臣之进退。实为狼狈。臣之年衰病深。难以供职之状。前后毕陈。而 圣上之所洞烛也。臣下来之日。 元子以臣侍讲日久。眷眷以 上教。申以从速上来之意。臣自念癃疾。必不堪道途之勤。故谨以前日所陈于 圣上者。复达于 元子。然退出 宫门。不胜犬马之恋。几于出涕也。臣之齿发。不至如今日之衰。则侍讲数年。获睹 睿学之成就者。是臣之至愿。而能事亦毕矣。惟是遭逢太晚。暮景迫人。聪明筋力。月异而岁不同。较去岁休暇之日则亦大相远矣。臣只自抚躬悲叹而已。臣既不能前进。而所授职名尚存。风宪之地。不可久旷。伏望 圣慈谅臣愚恳。 特许解职。俾遂休退之志。以尽馀年。不胜幸甚。臣无任激切屏营之至。谨昧死以 闻。
辞执义。仍陈十三事疏。(甲子六月)
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18H 页
 伏以臣曩陈微恳。吐出肺肝。冀 赐骸骨。待尽丘壑。不自意 圣明不弃旧物。复下 召命。误恩稠叠。日以益隆。臣承 命兢惶。罔知所措。臣实世禄之遗荫也。自少多在仕路。初非洁身乱伦之流。岂有遭遇 明时。而乐为退藏。辜恩负德。自蹈于逋慢之诛乎。臣之老羸癃疾。决难仕职之状。前后毕陈。 圣上之所洞烛也。而然且 召之不置。未许休退者。岂不以臣之筋力。犹未尽耗。或可从事于末班也欤。顾臣躯壳虽存。而荣卫内竭。只是一偶人耳。聪明日减于畴曩。死亡将迫于朝夕。如是而贪恋 恩眷。往来不惮。无益于 国。取讥于人。实非臣之初心。亦岂非 国家之羞也。是以。臣外惧物议。内怀廉耻。自计已熟。拟全晚节。此外不敢复有他念也。况臣所带职名。寔系风宪。而自臣辞退以来。已阅旬月于田野之间。亦非公私所宜。伏愿 圣慈特谅愚衷。速 赐递免。丏臣将死之命。俾遂丘壑之志。千万幸甚。仍窃惟念。臣终始受 恩。无丝毫报答。今此远离。不胜恋 阙之怀。万一溘先朝露则徒抱泉下之恨矣。是以。不揆愚陋。略具一劄。条陈十三事。庸替 殿陛之对。伏惟 殿下垂察焉。一曰立大本。二曰恢旧业。三曰尊洪范。四曰
伏以臣曩陈微恳。吐出肺肝。冀 赐骸骨。待尽丘壑。不自意 圣明不弃旧物。复下 召命。误恩稠叠。日以益隆。臣承 命兢惶。罔知所措。臣实世禄之遗荫也。自少多在仕路。初非洁身乱伦之流。岂有遭遇 明时。而乐为退藏。辜恩负德。自蹈于逋慢之诛乎。臣之老羸癃疾。决难仕职之状。前后毕陈。 圣上之所洞烛也。而然且 召之不置。未许休退者。岂不以臣之筋力。犹未尽耗。或可从事于末班也欤。顾臣躯壳虽存。而荣卫内竭。只是一偶人耳。聪明日减于畴曩。死亡将迫于朝夕。如是而贪恋 恩眷。往来不惮。无益于 国。取讥于人。实非臣之初心。亦岂非 国家之羞也。是以。臣外惧物议。内怀廉耻。自计已熟。拟全晚节。此外不敢复有他念也。况臣所带职名。寔系风宪。而自臣辞退以来。已阅旬月于田野之间。亦非公私所宜。伏愿 圣慈特谅愚衷。速 赐递免。丏臣将死之命。俾遂丘壑之志。千万幸甚。仍窃惟念。臣终始受 恩。无丝毫报答。今此远离。不胜恋 阙之怀。万一溘先朝露则徒抱泉下之恨矣。是以。不揆愚陋。略具一劄。条陈十三事。庸替 殿陛之对。伏惟 殿下垂察焉。一曰立大本。二曰恢旧业。三曰尊洪范。四曰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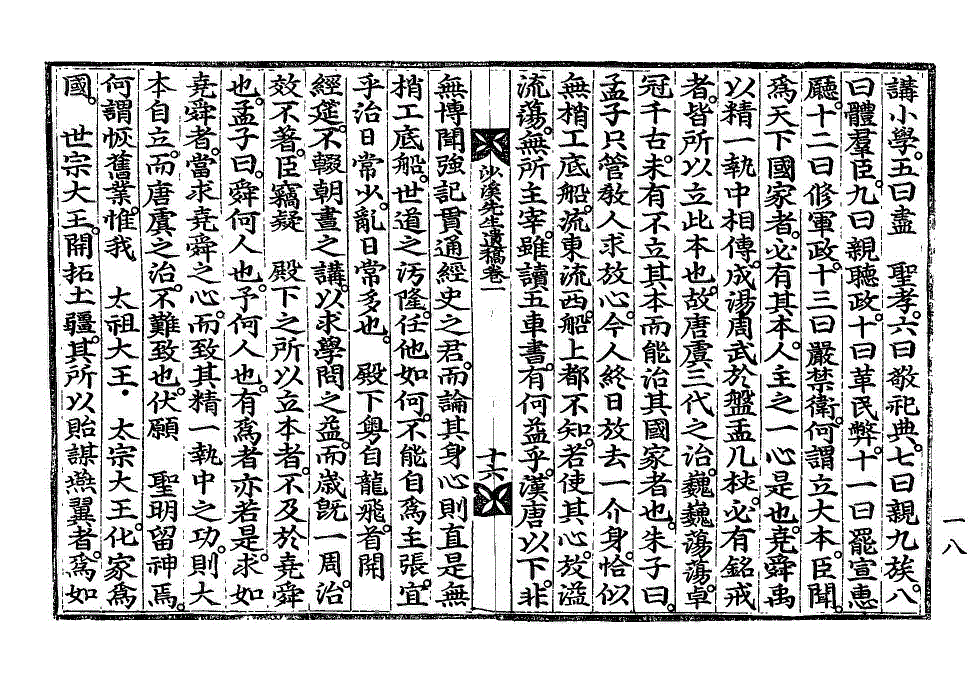 讲小学。五曰尽 圣孝。六曰敬祀典。七曰亲九族。八曰体群臣。九曰亲听政。十曰革民弊。十一曰罢宣惠厅。十二曰修军政。十三曰严禁卫。何谓立大本。臣闻。为天下国家者。必有其本。人主之一心是也。尧舜禹以精一执中相传。成汤周武于盘盂几杖。必有铭戒者。皆所以立此本也。故唐虞三代之治。巍巍荡荡。卓冠千古。未有不立其本而能治其国家者也。朱子曰。孟子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终日放去一介身。恰似无梢工底船。流东流西。船上都不知。若使其心。放溢流荡。无所主宰。虽读五车书。有何益乎。汉唐以下。非无博闻强记贯通经史之君。而论其身心则直是无梢工底船。世道之污隆。任他如何。不能自为主张。宜乎治日常少。乱日常多也。 殿下粤自龙飞。首开 经筵。不辍朝昼之讲。以求学问之益。而岁既一周。治效不著。臣窃疑 殿下之所以立本者。不及于尧舜也。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求如尧舜者。当求尧舜之心。而致其精一执中之功。则大本自立。而唐虞之治。不难致也。伏愿 圣明留神焉。何谓恢旧业。惟我 太祖大王 ,太宗大王。化家为国。 世宗大王。开拓土疆。其所以贻谋燕翼者。为如
讲小学。五曰尽 圣孝。六曰敬祀典。七曰亲九族。八曰体群臣。九曰亲听政。十曰革民弊。十一曰罢宣惠厅。十二曰修军政。十三曰严禁卫。何谓立大本。臣闻。为天下国家者。必有其本。人主之一心是也。尧舜禹以精一执中相传。成汤周武于盘盂几杖。必有铭戒者。皆所以立此本也。故唐虞三代之治。巍巍荡荡。卓冠千古。未有不立其本而能治其国家者也。朱子曰。孟子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终日放去一介身。恰似无梢工底船。流东流西。船上都不知。若使其心。放溢流荡。无所主宰。虽读五车书。有何益乎。汉唐以下。非无博闻强记贯通经史之君。而论其身心则直是无梢工底船。世道之污隆。任他如何。不能自为主张。宜乎治日常少。乱日常多也。 殿下粤自龙飞。首开 经筵。不辍朝昼之讲。以求学问之益。而岁既一周。治效不著。臣窃疑 殿下之所以立本者。不及于尧舜也。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求如尧舜者。当求尧舜之心。而致其精一执中之功。则大本自立。而唐虞之治。不难致也。伏愿 圣明留神焉。何谓恢旧业。惟我 太祖大王 ,太宗大王。化家为国。 世宗大王。开拓土疆。其所以贻谋燕翼者。为如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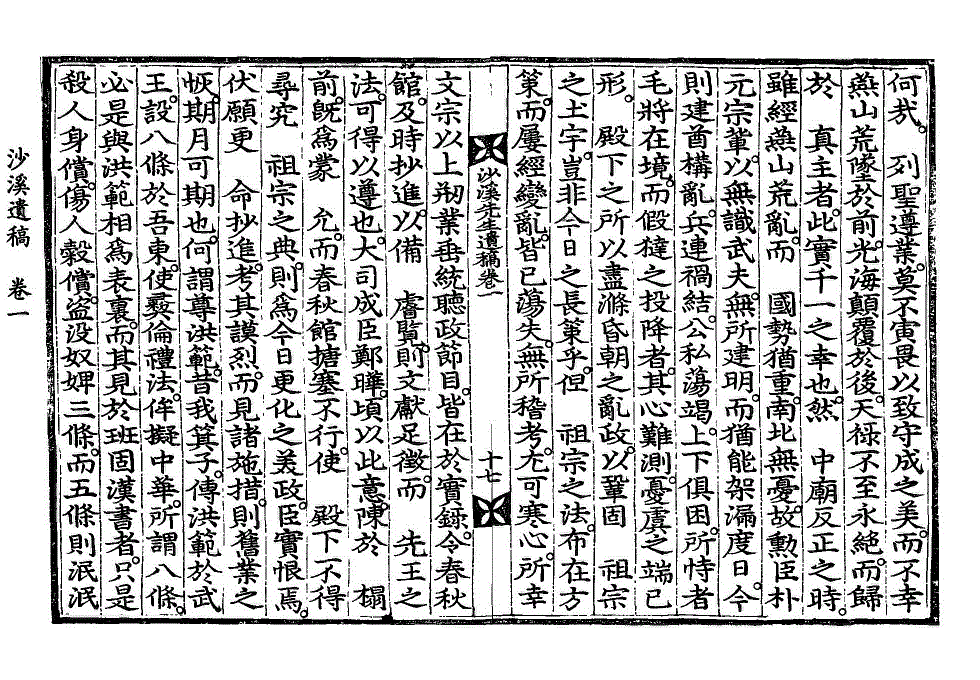 何哉。 列圣遵业。莫不寅畏以致守成之美。而不幸燕山荒坠于前。光海颠覆于后。天禄不至永绝。而归于 真主者。此实千一之幸也。然 中庙反正之时。虽经燕山荒乱。而 国势犹重。南北无忧。故勋臣朴元宗辈。以无识武夫。无所建明。而犹能架漏度日。今则建酋构乱。兵连祸结。公私荡竭。上下俱困。所恃者毛将在境。而假獭之投降者。其心难测。忧虞之端已形。 殿下之所以尽涤昏朝之乱政。以巩固 祖宗之土宇。岂非今日之长策乎。但 祖宗之法。布在方策。而屡经变乱。皆已荡失。无所稽考。尤可寒心。所幸文宗以上创业垂统听政节目。皆在于实录。令春秋馆。及时抄进。以备 睿览。则文献足徵。而 先王之法。可得以遵也。大司成臣郑晔。顷以此意。陈于 榻前。既为蒙 允。而春秋馆搪塞不行。使 殿下不得寻究 祖宗之典。则为今日更化之美政。臣实恨焉。伏愿更 命抄进。考其谟烈。而见诸施措。则旧业之恢。期月可期也。何谓尊洪范。昔我箕子。传洪范于武王。设八条于吾东。使彝伦礼法。侔拟中华。所谓八条。必是与洪范相为表里。而其见于班固汉书者。只是杀人身偿。伤人谷偿。盗没奴婢三条。而五条则泯泯
何哉。 列圣遵业。莫不寅畏以致守成之美。而不幸燕山荒坠于前。光海颠覆于后。天禄不至永绝。而归于 真主者。此实千一之幸也。然 中庙反正之时。虽经燕山荒乱。而 国势犹重。南北无忧。故勋臣朴元宗辈。以无识武夫。无所建明。而犹能架漏度日。今则建酋构乱。兵连祸结。公私荡竭。上下俱困。所恃者毛将在境。而假獭之投降者。其心难测。忧虞之端已形。 殿下之所以尽涤昏朝之乱政。以巩固 祖宗之土宇。岂非今日之长策乎。但 祖宗之法。布在方策。而屡经变乱。皆已荡失。无所稽考。尤可寒心。所幸文宗以上创业垂统听政节目。皆在于实录。令春秋馆。及时抄进。以备 睿览。则文献足徵。而 先王之法。可得以遵也。大司成臣郑晔。顷以此意。陈于 榻前。既为蒙 允。而春秋馆搪塞不行。使 殿下不得寻究 祖宗之典。则为今日更化之美政。臣实恨焉。伏愿更 命抄进。考其谟烈。而见诸施措。则旧业之恢。期月可期也。何谓尊洪范。昔我箕子。传洪范于武王。设八条于吾东。使彝伦礼法。侔拟中华。所谓八条。必是与洪范相为表里。而其见于班固汉书者。只是杀人身偿。伤人谷偿。盗没奴婢三条。而五条则泯泯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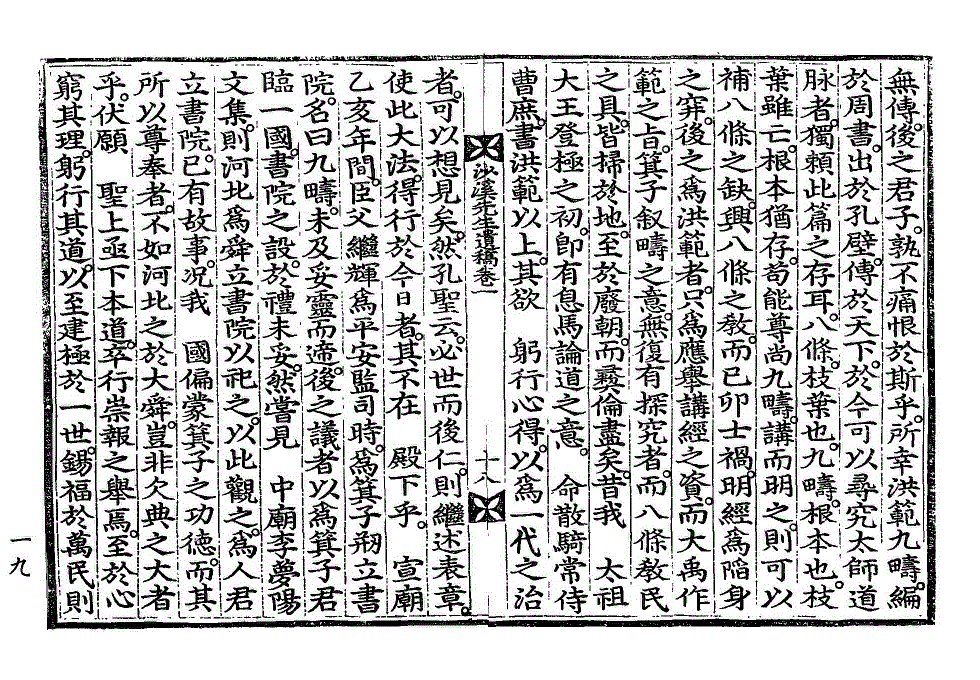 无传。后之君子。孰不痛恨于斯乎。所幸洪范九畴。编于周书。出于孔壁。传于天下。于今可以寻究太师道脉者。独赖此篇之存耳。八条。枝弃也。九畴。根本也。枝叶虽亡。根本犹存。苟能尊尚九畴。讲而明之。则可以补八条之缺。兴八条之教。而己卯士祸。明经为陷身之阱。后之为洪范者。只为应举讲经之资。而大禹作范之旨。箕子叙畴之意。无复有探究者。而八条教民之具。皆扫于地。至于废朝。而彝伦尽矣。昔我 太祖大王登极之初。即有息马论道之意。命散骑常侍曹庶。书洪范以上。其欲 躬行心得。以为一代之治者。可以想见矣。然孔圣云。必世而后仁。则继述表章。使此大法。得行于今日者。其不在 殿下乎。 宣庙乙亥年间。臣父继辉为平安监司时。为箕子刱立书院。名曰九畴。未及妥灵而递。后之议者以为箕子君临一国。书院之设。于礼未妥。然尝见 中庙李梦阳文集。则河北为舜立书院以祀之。以此观之。为人君立书院。已有故事。况我 国偏蒙箕子之功德。而其所以尊奉者。不如河北之于大舜。岂非欠典之大者乎。伏愿 圣上亟下本道。卒行崇报之举焉。至于心穷其理。躬行其道。以至建极于一世。锡福于万民则
无传。后之君子。孰不痛恨于斯乎。所幸洪范九畴。编于周书。出于孔壁。传于天下。于今可以寻究太师道脉者。独赖此篇之存耳。八条。枝弃也。九畴。根本也。枝叶虽亡。根本犹存。苟能尊尚九畴。讲而明之。则可以补八条之缺。兴八条之教。而己卯士祸。明经为陷身之阱。后之为洪范者。只为应举讲经之资。而大禹作范之旨。箕子叙畴之意。无复有探究者。而八条教民之具。皆扫于地。至于废朝。而彝伦尽矣。昔我 太祖大王登极之初。即有息马论道之意。命散骑常侍曹庶。书洪范以上。其欲 躬行心得。以为一代之治者。可以想见矣。然孔圣云。必世而后仁。则继述表章。使此大法。得行于今日者。其不在 殿下乎。 宣庙乙亥年间。臣父继辉为平安监司时。为箕子刱立书院。名曰九畴。未及妥灵而递。后之议者以为箕子君临一国。书院之设。于礼未妥。然尝见 中庙李梦阳文集。则河北为舜立书院以祀之。以此观之。为人君立书院。已有故事。况我 国偏蒙箕子之功德。而其所以尊奉者。不如河北之于大舜。岂非欠典之大者乎。伏愿 圣上亟下本道。卒行崇报之举焉。至于心穷其理。躬行其道。以至建极于一世。锡福于万民则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20H 页
 不外于 殿下之自勉。伏愿 圣明留神焉。且今世书院。如名贤中人所矜式者。后学之崇奉宜矣。如郑介清,郭诗之类。凭藉势力。亦且滥厕于其间。故是非不明。弊端不赀。今宜一从公论。有所财处也。何谓讲小学。古者教人之法。不过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而但见于曲礼,内则,弟子职诸篇。其全书则自经秦火。世不复见。而教亦蔑矣。惟我朱子蒐辑三代以上圣贤言行之关于立教,明伦,敬身者。为小学内篇。又取汉唐以下诸人言行为外篇。合内外而观之。则真是做人底样子。而为大学之阶梯。故 中庙朝儒臣赵光祖等。尊信此书。进讲于 经筵。而又刊布民间。必使学者先习而行之。故四方风动。庶几尧舜君民之治。此正箕子以后千载一时。而不幸遭祸。道不终行。此志士之所以扼腕流涕。继之以血者也。臣师臣李珥在 宣庙朝。亦讲明是书。以追己卯之馀风。至于纂集诸家之注。为之折衷。以教后学。以为风化之基矣。殿下潜心此书。并以李珥所定注说。进讲于 经筵。以收风行草偃之效焉。不胜幸甚。但小学是朱子所撰。故朱子言行则不编于其中。使后学不得取则。诚可恨也。臣韩峤曾以此。质于其师成浑。而撮其言行
不外于 殿下之自勉。伏愿 圣明留神焉。且今世书院。如名贤中人所矜式者。后学之崇奉宜矣。如郑介清,郭诗之类。凭藉势力。亦且滥厕于其间。故是非不明。弊端不赀。今宜一从公论。有所财处也。何谓讲小学。古者教人之法。不过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而但见于曲礼,内则,弟子职诸篇。其全书则自经秦火。世不复见。而教亦蔑矣。惟我朱子蒐辑三代以上圣贤言行之关于立教,明伦,敬身者。为小学内篇。又取汉唐以下诸人言行为外篇。合内外而观之。则真是做人底样子。而为大学之阶梯。故 中庙朝儒臣赵光祖等。尊信此书。进讲于 经筵。而又刊布民间。必使学者先习而行之。故四方风动。庶几尧舜君民之治。此正箕子以后千载一时。而不幸遭祸。道不终行。此志士之所以扼腕流涕。继之以血者也。臣师臣李珥在 宣庙朝。亦讲明是书。以追己卯之馀风。至于纂集诸家之注。为之折衷。以教后学。以为风化之基矣。殿下潜心此书。并以李珥所定注说。进讲于 经筵。以收风行草偃之效焉。不胜幸甚。但小学是朱子所撰。故朱子言行则不编于其中。使后学不得取则。诚可恨也。臣韩峤曾以此。质于其师成浑。而撮其言行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20L 页
 之最关者。编成一书。成浑死后。令臣證订。臣取而观之。无非格言至论有关于世教者也。伏愿 殿下特命缮写以进。以备 睿览。且令 元子俟文义稍通。与小学兼看。则必有所益也。何谓尽 圣孝。夫孝者。百行之源。孔子所谓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者是也。 殿下奉 大妃于十年幽闭之馀。御于法宫。婉容愉色。 视膳问安。未尝少怠。一国耸动。孰不谓 圣人之大孝乎。杨子曰。事亲自知其不足者。其舜乎。若以为吾孝已尽。则便不是圣人之孝也。 殿下亦当常存不足之心。一日十二时。点检吾之所以事亲。有不如大舜者乎。如有一毫未尽分处。怵然警省。益致其诚。则止孝止慈。各尽其道。兆民之观感。鸟兽之生育。皆本于此矣。伏愿 殿下留神焉。何谓敬祀典。古之帝王。其于宗庙祭享。必尽其诚敬。故天子亲耕以备粢盛。王后亲蚕以供祭服。先儒以为天下非无良农工女也。不若自亲其致敬尽礼之实也。盖天子诸侯。各有养兽之官。及至岁时。斋戒沐浴。纳其犠牷牲而视之。择其毛而卜之吉。然后养之。月朔及月半。君必巡牲。将祭。君必牵牲。将杀。君执銮刀。取肝以膋。此乃重宗庙血食而不敢不敬也。然后
之最关者。编成一书。成浑死后。令臣證订。臣取而观之。无非格言至论有关于世教者也。伏愿 殿下特命缮写以进。以备 睿览。且令 元子俟文义稍通。与小学兼看。则必有所益也。何谓尽 圣孝。夫孝者。百行之源。孔子所谓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者是也。 殿下奉 大妃于十年幽闭之馀。御于法宫。婉容愉色。 视膳问安。未尝少怠。一国耸动。孰不谓 圣人之大孝乎。杨子曰。事亲自知其不足者。其舜乎。若以为吾孝已尽。则便不是圣人之孝也。 殿下亦当常存不足之心。一日十二时。点检吾之所以事亲。有不如大舜者乎。如有一毫未尽分处。怵然警省。益致其诚。则止孝止慈。各尽其道。兆民之观感。鸟兽之生育。皆本于此矣。伏愿 殿下留神焉。何谓敬祀典。古之帝王。其于宗庙祭享。必尽其诚敬。故天子亲耕以备粢盛。王后亲蚕以供祭服。先儒以为天下非无良农工女也。不若自亲其致敬尽礼之实也。盖天子诸侯。各有养兽之官。及至岁时。斋戒沐浴。纳其犠牷牲而视之。择其毛而卜之吉。然后养之。月朔及月半。君必巡牲。将祭。君必牵牲。将杀。君执銮刀。取肝以膋。此乃重宗庙血食而不敢不敬也。然后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21H 页
 祖考享之而子孙受其福。孔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又曰。我祭则受福。伏愿 殿下以古礼为必可行。以圣训为必可法。非有军国大事。皆必 亲莅。陟降庭止。见其昭临。有故则虽使摄行。必致其如不祭之诚。则 祖宗默佑。上天降嘏。必有寿考万年。锡羡无疆之庆矣。何谓亲九族。昔尧之治天下。九族既睦。然后及于平章。大学传曰。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安有家道坏乱而能保其国者哉。九族虽有亲疏。自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况兄弟姊妹。其初则父之一身也。父之兄弟。其初则祖之一身也。良知良能。仁爱至情。若不因此而推之。何能以施及于兆民也。汉文之斗粟兴谣。司马氏之骨肉相残。可以鉴矣。而光海无道。贼臣怂恿。大狱屡起。同气并残。此国人之所共愤。而 殿下之所恻怛者也。仁城君珙与逆瑅。同出贼招。 殿下特下不问推戴之 教。以为全安之地。其恩可谓罔极。而逆瑅不念再生之德。投入贼适。为其拥立。至于贼败之后。与贼同走。被擒就死。此则人人所得而诛者也。沈器远之所为。未为不可也。延平府院君臣李贵。因此并疑仁城。乃举其光海时请从河仁俊
祖考享之而子孙受其福。孔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又曰。我祭则受福。伏愿 殿下以古礼为必可行。以圣训为必可法。非有军国大事。皆必 亲莅。陟降庭止。见其昭临。有故则虽使摄行。必致其如不祭之诚。则 祖宗默佑。上天降嘏。必有寿考万年。锡羡无疆之庆矣。何谓亲九族。昔尧之治天下。九族既睦。然后及于平章。大学传曰。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安有家道坏乱而能保其国者哉。九族虽有亲疏。自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况兄弟姊妹。其初则父之一身也。父之兄弟。其初则祖之一身也。良知良能。仁爱至情。若不因此而推之。何能以施及于兆民也。汉文之斗粟兴谣。司马氏之骨肉相残。可以鉴矣。而光海无道。贼臣怂恿。大狱屡起。同气并残。此国人之所共愤。而 殿下之所恻怛者也。仁城君珙与逆瑅。同出贼招。 殿下特下不问推戴之 教。以为全安之地。其恩可谓罔极。而逆瑅不念再生之德。投入贼适。为其拥立。至于贼败之后。与贼同走。被擒就死。此则人人所得而诛者也。沈器远之所为。未为不可也。延平府院君臣李贵。因此并疑仁城。乃举其光海时请从河仁俊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21L 页
 凶疏及诸贼之乱言。上劄请罪。而与副提学臣郑经世。论议不合。互上章劄。是非纷纭。臣以为不有李贵之言。则宗戚横恣。其身将陷于罪恶。不有经世之议。则少涉疑似。骨肉便至于难保。伏愿 殿下执其两端。察二人之言皆出于为国。而为之调剂。俾无朝著携贰之祸。且思保全懿亲之道。而又于燕闲之暇。时接宗班。赐以温颜。厚其赐予。以尽家人之礼。使无疑阻之心。则齐家之道。亶在于是。平章协和之化。可以此而推之矣。何谓体群臣。所谓体者。设以身处其地。而察其心之好恶也。盖君如元首。臣如股肱。分有尊卑。而义则一体。此所以忠信以待之。重禄以养之也。然禄不足。则有乖忠信之道而不可以劝士也。谨按。新罗之地。乃吾东三分之一。而待其臣金庾信极其优厚。其生也重其禄。其死也岁给其妻以千石之租。高丽员外之禄。至于百石。员外即今之郎僚也。其禄之厚如此。而死后皆给其妻以守身田。使免饥馁。 国朝亦以是法。载于经济六典。而今亡矣。 中庙朝儒臣金安国建请复行。而竟不得施。今者因乱。有每朔给料之例。合三朔所给。而颁于四孟。名曰颁禄。近日四孟所给。亦不能继。臣僚艰苦之状。有难胜言。廉
凶疏及诸贼之乱言。上劄请罪。而与副提学臣郑经世。论议不合。互上章劄。是非纷纭。臣以为不有李贵之言。则宗戚横恣。其身将陷于罪恶。不有经世之议。则少涉疑似。骨肉便至于难保。伏愿 殿下执其两端。察二人之言皆出于为国。而为之调剂。俾无朝著携贰之祸。且思保全懿亲之道。而又于燕闲之暇。时接宗班。赐以温颜。厚其赐予。以尽家人之礼。使无疑阻之心。则齐家之道。亶在于是。平章协和之化。可以此而推之矣。何谓体群臣。所谓体者。设以身处其地。而察其心之好恶也。盖君如元首。臣如股肱。分有尊卑。而义则一体。此所以忠信以待之。重禄以养之也。然禄不足。则有乖忠信之道而不可以劝士也。谨按。新罗之地。乃吾东三分之一。而待其臣金庾信极其优厚。其生也重其禄。其死也岁给其妻以千石之租。高丽员外之禄。至于百石。员外即今之郎僚也。其禄之厚如此。而死后皆给其妻以守身田。使免饥馁。 国朝亦以是法。载于经济六典。而今亡矣。 中庙朝儒臣金安国建请复行。而竟不得施。今者因乱。有每朔给料之例。合三朔所给。而颁于四孟。名曰颁禄。近日四孟所给。亦不能继。臣僚艰苦之状。有难胜言。廉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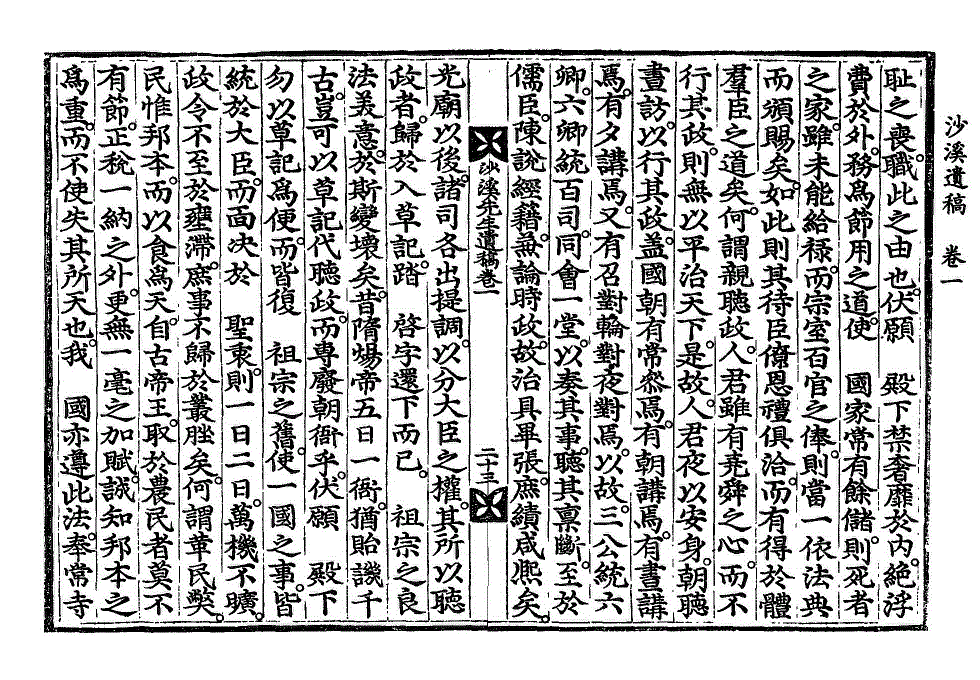 耻之丧。职此之由也。伏愿 殿下禁奢靡于内。绝浮费于外。务为节用之道。使 国家常有馀储。则死者之家。虽未能给禄。而宗室百官之俸。则当一依法典而颁赐矣。如此则其待臣僚恩礼俱洽。而有得于体群臣之道矣。何谓亲听政。人君虽有尧舜之心。而不行其政。则无以平治天下。是故。人君夜以安身。朝听昼访。以行其政。盖国朝有常参焉。有朝讲焉。有昼讲焉。有夕讲焉。又有召对,轮对,夜对焉。以故。三公统六卿。六卿统百司。同会一堂。以奏其事。听其禀断。至于儒臣。陈说经籍。兼论时政。故治具毕张。庶绩咸熙矣。光庙以后。诸司各出提调。以分大臣之权。其所以听政者。归于入草记。踏 启字还下而已。 祖宗之良法美意。于斯变坏矣。昔隋焬帝五日一衙。犹贻讥千古。岂可以草记代听政。而专废朝衙乎。伏愿 殿下勿以草记为便。而皆复 祖宗之旧。使一国之事。皆统于大臣。而面决于 圣衷。则一日二日。万机不旷。政令不至于壅滞。庶事不归于丛脞矣。何谓革民弊。民惟邦本。而以食为天。自古帝王。取于农民者莫不有节。正税一纳之外。更无一毫之加赋。诚知邦本之为重。而不使失其所天也。我 国亦遵此法。奉常寺
耻之丧。职此之由也。伏愿 殿下禁奢靡于内。绝浮费于外。务为节用之道。使 国家常有馀储。则死者之家。虽未能给禄。而宗室百官之俸。则当一依法典而颁赐矣。如此则其待臣僚恩礼俱洽。而有得于体群臣之道矣。何谓亲听政。人君虽有尧舜之心。而不行其政。则无以平治天下。是故。人君夜以安身。朝听昼访。以行其政。盖国朝有常参焉。有朝讲焉。有昼讲焉。有夕讲焉。又有召对,轮对,夜对焉。以故。三公统六卿。六卿统百司。同会一堂。以奏其事。听其禀断。至于儒臣。陈说经籍。兼论时政。故治具毕张。庶绩咸熙矣。光庙以后。诸司各出提调。以分大臣之权。其所以听政者。归于入草记。踏 启字还下而已。 祖宗之良法美意。于斯变坏矣。昔隋焬帝五日一衙。犹贻讥千古。岂可以草记代听政。而专废朝衙乎。伏愿 殿下勿以草记为便。而皆复 祖宗之旧。使一国之事。皆统于大臣。而面决于 圣衷。则一日二日。万机不旷。政令不至于壅滞。庶事不归于丛脞矣。何谓革民弊。民惟邦本。而以食为天。自古帝王。取于农民者莫不有节。正税一纳之外。更无一毫之加赋。诚知邦本之为重。而不使失其所天也。我 国亦遵此法。奉常寺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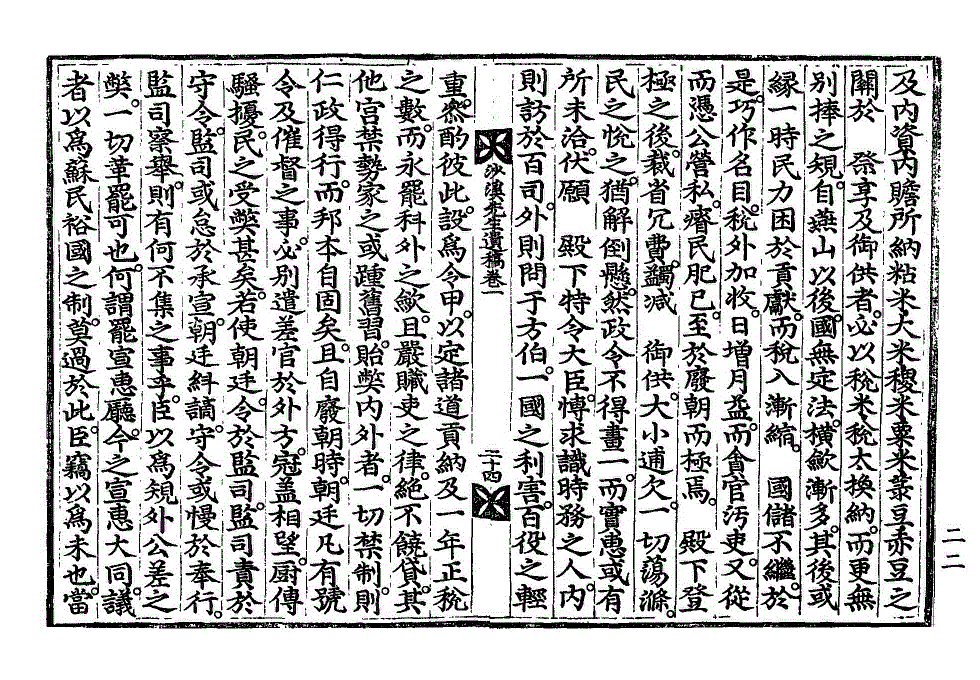 及内资,内赡所纳粘米,大米,稷米,粟米,菉豆,赤豆之关于 祭享及御供者。必以税米,税太换纳。而更无别捧之规。自燕山以后。国无定法。横敛渐多。其后或缘一时民力困于贡献。而税入渐缩。 国储不继。于是。巧作名目。税外加收。日增月益。而贪官污吏。又从而凭公营私。瘠民肥己。至于废朝而极焉。 殿下登极之后。裁省冗费。蠲减 御供。大小逋欠。一切荡涤。民之悦之。犹解倒悬。然政令不得画一。而实惠或有所未洽。伏愿 殿下特令大臣。博求识时务之人。内则访于百司。外则问于方伯。一国之利害。百役之轻重。参酌彼此。设为令甲。以定诸道贡纳及一年正税之数。而永罢科外之敛。且严赃吏之律。绝不饶贷。其他宫禁势家之或踵旧习。贻弊内外者。一切禁制。则仁政得行。而邦本自固矣。且自庙朝时。朝廷凡有号令及催督之事。必别遣差官于外方。冠盖相望。厨传骚扰。民之受弊甚矣。若使朝廷。令于监司。监司责于守令。监司或怠于承宣。朝廷紏谪。守令或慢于奉行。监司察举。则有何不集之事乎。臣以为规外公差之弊。一切革罢可也。何谓罢宣惠厅。今之宣惠大同。议者以为苏民裕国之制。莫过于此。臣窃以为未也。当
及内资,内赡所纳粘米,大米,稷米,粟米,菉豆,赤豆之关于 祭享及御供者。必以税米,税太换纳。而更无别捧之规。自燕山以后。国无定法。横敛渐多。其后或缘一时民力困于贡献。而税入渐缩。 国储不继。于是。巧作名目。税外加收。日增月益。而贪官污吏。又从而凭公营私。瘠民肥己。至于废朝而极焉。 殿下登极之后。裁省冗费。蠲减 御供。大小逋欠。一切荡涤。民之悦之。犹解倒悬。然政令不得画一。而实惠或有所未洽。伏愿 殿下特令大臣。博求识时务之人。内则访于百司。外则问于方伯。一国之利害。百役之轻重。参酌彼此。设为令甲。以定诸道贡纳及一年正税之数。而永罢科外之敛。且严赃吏之律。绝不饶贷。其他宫禁势家之或踵旧习。贻弊内外者。一切禁制。则仁政得行。而邦本自固矣。且自庙朝时。朝廷凡有号令及催督之事。必别遣差官于外方。冠盖相望。厨传骚扰。民之受弊甚矣。若使朝廷。令于监司。监司责于守令。监司或怠于承宣。朝廷紏谪。守令或慢于奉行。监司察举。则有何不集之事乎。臣以为规外公差之弊。一切革罢可也。何谓罢宣惠厅。今之宣惠大同。议者以为苏民裕国之制。莫过于此。臣窃以为未也。当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23H 页
 初大同之设。始于京畿。夫畿内则四面州县。不过一日二日之程。或以水运。或以陆运。其转输之劳。雇价之费。不至甚苦。且田皆五六等。故六七石落种之田。仅为一结。故土虽瘠薄。计其所收。则不下三四十斛。而只供春秋十六斗之米。此外无他徵敛。畿民之以为便者。盖以此也。若两湖则不然。以道里言之。则忠清近邑。才为畿甸远邑之次。而全罗道则或三倍于忠清道。其船运之价。虽自官画给。而海路险远。不幸覆败则或有再徵之患。以田结言之。土虽肥沃。结数甚高。故一石落种之田。已与京几六七石落种之田。同其结数矣。以此与京畿均供春秋十六斗之米。而远路雇价之费。比畿邑则又至于二三倍。此外又有月膳进上及三营所纳诸般刷马之役。种种叠出。疏数无定。轻重不等。抑而行之则民必不堪矣。当初则人皆谓更无他役矣。到今不然。事目之外。又有许多徵求。民之怨苦。势所然也。今年虽以凶歉。极加裁损。而其弊尚如此。后日稍稔。一以畿邑为准。则将见两湖公私之力。一时荡败矣。大抵徭役不均之弊。由于田结之失实。当初量田之时。任事之臣。不能详察。故吏胥品官。因缘舞弄。田虽沃饶。或以五六等悬录。田
初大同之设。始于京畿。夫畿内则四面州县。不过一日二日之程。或以水运。或以陆运。其转输之劳。雇价之费。不至甚苦。且田皆五六等。故六七石落种之田。仅为一结。故土虽瘠薄。计其所收。则不下三四十斛。而只供春秋十六斗之米。此外无他徵敛。畿民之以为便者。盖以此也。若两湖则不然。以道里言之。则忠清近邑。才为畿甸远邑之次。而全罗道则或三倍于忠清道。其船运之价。虽自官画给。而海路险远。不幸覆败则或有再徵之患。以田结言之。土虽肥沃。结数甚高。故一石落种之田。已与京几六七石落种之田。同其结数矣。以此与京畿均供春秋十六斗之米。而远路雇价之费。比畿邑则又至于二三倍。此外又有月膳进上及三营所纳诸般刷马之役。种种叠出。疏数无定。轻重不等。抑而行之则民必不堪矣。当初则人皆谓更无他役矣。到今不然。事目之外。又有许多徵求。民之怨苦。势所然也。今年虽以凶歉。极加裁损。而其弊尚如此。后日稍稔。一以畿邑为准。则将见两湖公私之力。一时荡败矣。大抵徭役不均之弊。由于田结之失实。当初量田之时。任事之臣。不能详察。故吏胥品官。因缘舞弄。田虽沃饶。或以五六等悬录。田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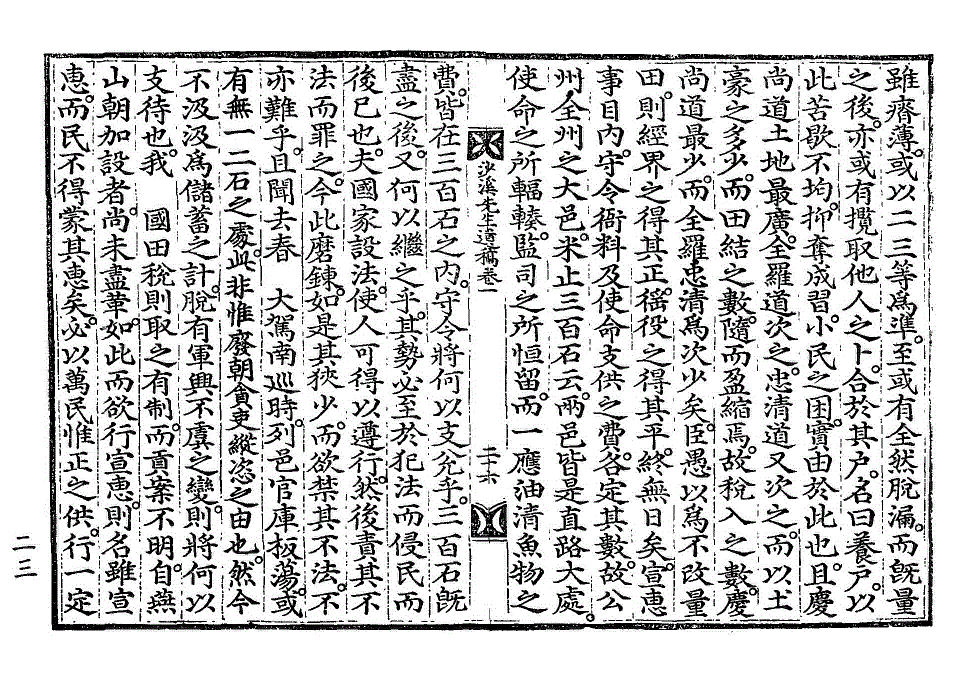 虽瘠薄。或以二三等为准。至或有全然脱漏。而既量之后。亦或有揽取他人之卜。合于其户。名曰养户。以此苦歇不均。抑夺成习。小民之困。实由于此也。且庆尚道土地最广。全罗道次之。忠清道又次之。而以土豪之多少。而田结之数。随而盈缩焉。故税入之数。庆尚道最少。而全罗,忠清为次少矣。臣愚以为不改量田。则经界之得其正。徭役之得其平。终无日矣。宣惠事目内。守令衙料及使命支供之费。各定其数。故公州,全州之大邑。米止三百石云。两邑皆是直路大处。使命之所辐辏。监司之所恒留。而一应油清鱼物之费。皆在三百石之内。守令将何以支兑乎。三百石既尽之后。又何以继之乎。其势必至于犯法而侵民而后已也。夫国家设法。使人可得以遵行。然后责其不法而罪之。今此磨鍊。如是其狭少。而欲禁其不法。不亦难乎。且闻去春 大驾南巡时。列邑官库板荡。或有无一二石之处。此非惟废朝贪吏纵恣之由也。然今不汲汲为储蓄之计。脱有军兴不虞之变。则将何以支待也。我 国田税则取之有制。而贡案不明。自燕山朝加设者。尚未尽革。如此而欲行宣惠。则名虽宣惠。而民不得蒙其惠矣。必以万民惟正之供。行一定
虽瘠薄。或以二三等为准。至或有全然脱漏。而既量之后。亦或有揽取他人之卜。合于其户。名曰养户。以此苦歇不均。抑夺成习。小民之困。实由于此也。且庆尚道土地最广。全罗道次之。忠清道又次之。而以土豪之多少。而田结之数。随而盈缩焉。故税入之数。庆尚道最少。而全罗,忠清为次少矣。臣愚以为不改量田。则经界之得其正。徭役之得其平。终无日矣。宣惠事目内。守令衙料及使命支供之费。各定其数。故公州,全州之大邑。米止三百石云。两邑皆是直路大处。使命之所辐辏。监司之所恒留。而一应油清鱼物之费。皆在三百石之内。守令将何以支兑乎。三百石既尽之后。又何以继之乎。其势必至于犯法而侵民而后已也。夫国家设法。使人可得以遵行。然后责其不法而罪之。今此磨鍊。如是其狭少。而欲禁其不法。不亦难乎。且闻去春 大驾南巡时。列邑官库板荡。或有无一二石之处。此非惟废朝贪吏纵恣之由也。然今不汲汲为储蓄之计。脱有军兴不虞之变。则将何以支待也。我 国田税则取之有制。而贡案不明。自燕山朝加设者。尚未尽革。如此而欲行宣惠。则名虽宣惠。而民不得蒙其惠矣。必以万民惟正之供。行一定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24H 页
 之法。以省浮费。节财用为先务。且择度支之官。委任而责成。然后宣惠之法行。而国用自裕矣。何谓修军政。我 国军兵给保之法。实本于古制也。甲士以上。为能射骑兵则上番之时。鍊才给禄。定虏卫以上则上番时。皆着冠带。同于士大夫。内禁卫才落者。以次降之。而以正兵以下取才入格者。升为定虏卫。以之升降劝惩。所以励军政者至矣。而又设广兴仓颁禄。军资仓养兵。有如高丽左仓右仓之规。而今则仓库皆空。百官颁禄。尚不能继则养兵一事。更无可望。驯至于区别其正兵及定虏卫,别侍卫,甲士等役之。皆如贱隶。故人之避军役。甚于虎口。加以国纲陵夷。名为两班。皆不得定军。军政尽废。已无奈何。伏愿 殿下特令兵曹。稍明军政。渐复 祖宗之旧焉。议者以为查整军民。禁民逃役。无过于号牌。号牌之法不行。则无以为军政。臣则窃以为不然。夫号牌始于何时。王道不行。而世降俗末。人心巧诈。有此不得已之计矣。然而法令虽善。国必有纪纲而后可行。如有纪纲。则凡事自能方方正正。条目自整。复何事于号牌。如无纪纲。则虽欲行号牌。而终不可得矣。商鞅之行法。犹且信赏必罚。而其民从之。卒致富强。由今日之纪
之法。以省浮费。节财用为先务。且择度支之官。委任而责成。然后宣惠之法行。而国用自裕矣。何谓修军政。我 国军兵给保之法。实本于古制也。甲士以上。为能射骑兵则上番之时。鍊才给禄。定虏卫以上则上番时。皆着冠带。同于士大夫。内禁卫才落者。以次降之。而以正兵以下取才入格者。升为定虏卫。以之升降劝惩。所以励军政者至矣。而又设广兴仓颁禄。军资仓养兵。有如高丽左仓右仓之规。而今则仓库皆空。百官颁禄。尚不能继则养兵一事。更无可望。驯至于区别其正兵及定虏卫,别侍卫,甲士等役之。皆如贱隶。故人之避军役。甚于虎口。加以国纲陵夷。名为两班。皆不得定军。军政尽废。已无奈何。伏愿 殿下特令兵曹。稍明军政。渐复 祖宗之旧焉。议者以为查整军民。禁民逃役。无过于号牌。号牌之法不行。则无以为军政。臣则窃以为不然。夫号牌始于何时。王道不行。而世降俗末。人心巧诈。有此不得已之计矣。然而法令虽善。国必有纪纲而后可行。如有纪纲。则凡事自能方方正正。条目自整。复何事于号牌。如无纪纲。则虽欲行号牌。而终不可得矣。商鞅之行法。犹且信赏必罚。而其民从之。卒致富强。由今日之纪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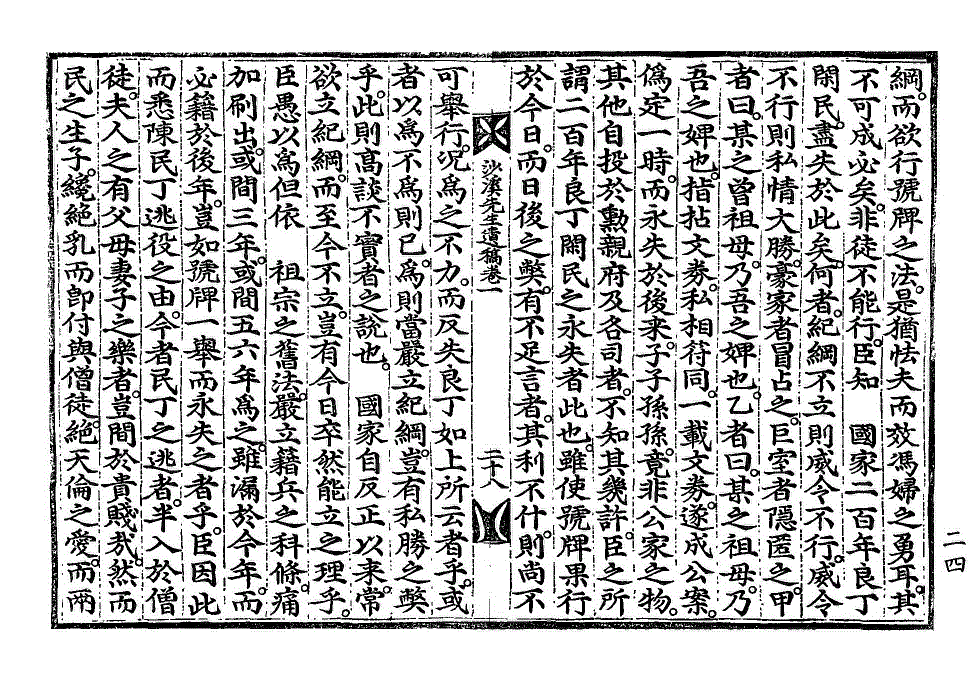 纲。而欲行号牌之法。是犹怯夫而效冯妇之勇耳。其不可成必矣。非徒不能行。臣知 国家二百年良丁闲民。尽失于此矣。何者。纪纲不立则威令不行。威令不行则私情大胜。豪家者冒占之。巨室者隐匿之。甲者曰。某之曾祖母。乃吾之婢也。乙者曰。某之祖母。乃吾之婢也。指拈文券。私相符同。一载文券。遂成公案。伪定一时。而永失于后来。子子孙孙。竟非公家之物。其他自投于勋亲府及各司者。不知其几许。臣之所谓二百年良丁闲民之永失者此也。虽使号牌果行于今日。而日后之弊。有不足言者。其利不什。则尚不可举行。况为之不力。而反失良丁如上所云者乎。或者以为不为则已。为则当严立纪纲。岂有私胜之弊乎。此则高谈不实者之说也。 国家自反正以来。常欲立纪纲。而至今不立。岂有今日卒然能立之理乎。臣愚以为但依 祖宗之旧法。严立籍兵之科条。痛加刷出。或间三年。或间五六年为之。虽漏于今年。而必籍于后年。岂如号牌一举而永失之者乎。臣因此而悉陈民丁逃役之由。今者民丁之逃者。半入于僧徒。夫人之有父母妻子之乐者。岂间于贵贱哉。然而民之生子。才绝乳而即付与僧徒。绝天伦之爱。而两
纲。而欲行号牌之法。是犹怯夫而效冯妇之勇耳。其不可成必矣。非徒不能行。臣知 国家二百年良丁闲民。尽失于此矣。何者。纪纲不立则威令不行。威令不行则私情大胜。豪家者冒占之。巨室者隐匿之。甲者曰。某之曾祖母。乃吾之婢也。乙者曰。某之祖母。乃吾之婢也。指拈文券。私相符同。一载文券。遂成公案。伪定一时。而永失于后来。子子孙孙。竟非公家之物。其他自投于勋亲府及各司者。不知其几许。臣之所谓二百年良丁闲民之永失者此也。虽使号牌果行于今日。而日后之弊。有不足言者。其利不什。则尚不可举行。况为之不力。而反失良丁如上所云者乎。或者以为不为则已。为则当严立纪纲。岂有私胜之弊乎。此则高谈不实者之说也。 国家自反正以来。常欲立纪纲。而至今不立。岂有今日卒然能立之理乎。臣愚以为但依 祖宗之旧法。严立籍兵之科条。痛加刷出。或间三年。或间五六年为之。虽漏于今年。而必籍于后年。岂如号牌一举而永失之者乎。臣因此而悉陈民丁逃役之由。今者民丁之逃者。半入于僧徒。夫人之有父母妻子之乐者。岂间于贵贱哉。然而民之生子。才绝乳而即付与僧徒。绝天伦之爱。而两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25H 页
 不相恤者。岂其性然哉。诚以不忍其赋役之烦故也。臣窃见军士上番。所收于其保者。不过十五六木匹。而祈寒暑雨暴露之苦。上司各衙门侵责之患。有不可堪耐。至于兵水营各镇浦分防者。则率皆除防捧价。 朝廷事目。虽以三匹为限。而必捧以升细尺长者。故其一匹。可当恒用六七匹矣。此外又有役事之价一二匹。通计一名所输。其数几何。或以一名之木六七匹。又有名为差备。以其当纳之木。贸纳白米,粘米,真荏,水荏等。而其所定之数。倍于元价。且徵于背节之时。故军士不胜其苦。欲为立番。而亦不许焉。盖兵水营各镇浦之所资以赖者。全在于此故也。至于公贱每年之贡。则只收一二匹。均是王民。而苦歇若是其悬殊。此岂王政之所宜乎。平常无事之时。怨气盈腹。而缓急之际。又且驱于死地。民之逃役。如避虎口者。不亦宜乎。夫兵。死地也。虽惠养之得其道。犹恐致力之不尽。况困苦侵渔之害。至于此极。而敢望其亲上死长之效乎。曾子曰。出乎尔者。反乎尔者。可不惧哉。臣愚以为宜令朝廷。别思优惠之方。其惠足以养其身及其妻子。身虽奔命于其役。而上之惠可以代其耕。使人人皆愿为军兵。然后庶得其死力矣。然
不相恤者。岂其性然哉。诚以不忍其赋役之烦故也。臣窃见军士上番。所收于其保者。不过十五六木匹。而祈寒暑雨暴露之苦。上司各衙门侵责之患。有不可堪耐。至于兵水营各镇浦分防者。则率皆除防捧价。 朝廷事目。虽以三匹为限。而必捧以升细尺长者。故其一匹。可当恒用六七匹矣。此外又有役事之价一二匹。通计一名所输。其数几何。或以一名之木六七匹。又有名为差备。以其当纳之木。贸纳白米,粘米,真荏,水荏等。而其所定之数。倍于元价。且徵于背节之时。故军士不胜其苦。欲为立番。而亦不许焉。盖兵水营各镇浦之所资以赖者。全在于此故也。至于公贱每年之贡。则只收一二匹。均是王民。而苦歇若是其悬殊。此岂王政之所宜乎。平常无事之时。怨气盈腹。而缓急之际。又且驱于死地。民之逃役。如避虎口者。不亦宜乎。夫兵。死地也。虽惠养之得其道。犹恐致力之不尽。况困苦侵渔之害。至于此极。而敢望其亲上死长之效乎。曾子曰。出乎尔者。反乎尔者。可不惧哉。臣愚以为宜令朝廷。别思优惠之方。其惠足以养其身及其妻子。身虽奔命于其役。而上之惠可以代其耕。使人人皆愿为军兵。然后庶得其死力矣。然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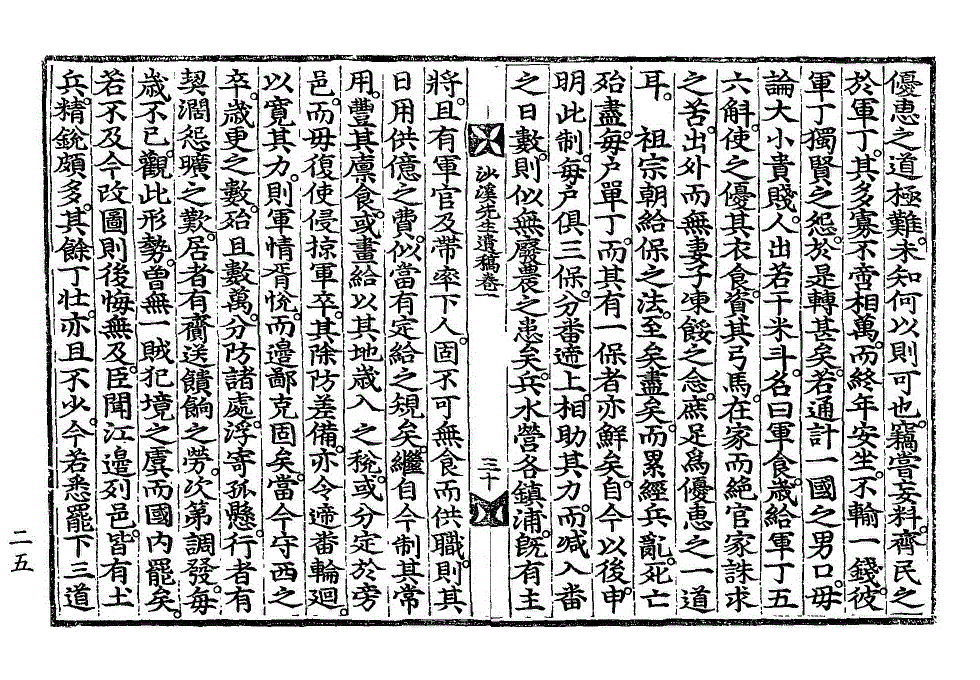 优惠之道极难。未知何以则可也。窃尝妄料。齐民之于军丁。其多寡不啻相万。而终年安坐。不输一钱。彼军丁独贤之怨。于是转甚矣。若通计一国之男口。毋论大小贵贱。人出若干米斗。名曰军食。岁给军丁五六斛。使之优其衣食。资其弓马。在家而绝官家诛求之苦。出外而无妻子冻馁之念。庶足为优惠之一道耳。 祖宗朝给保之法。至矣尽矣。而累经兵乱。死亡殆尽。每户单丁。而其有一保者亦鲜矣。自今以后。申明此制。每户俱三保。分番递上。相助其力。而减入番之日数。则似无废农之患矣。兵水营各镇浦。既有主将。且有军官及带率下人。固不可无食而供职。则其日用供亿之费。似当有定给之规矣。继自今制其常用。丰其廪食。或画给以其地岁入之税。或分定于旁邑。而毋复使侵掠军卒。其除防差备。亦令递番轮回。以宽其力。则军情胥悦。而边鄙克固矣。当今守西之卒。岁更之数。殆且数万。分防诸处。浮寄孤悬。行者有契阔怨旷之叹。居者有赍送馈饷之劳。次第调发。每岁不已。观此形势。曾无一贼犯境之虞而国内罢矣。若不及今改图则后悔无及。臣闻江边列邑。皆有土兵。精锐颇多。其馀丁壮。亦且不少。今若悉罢下三道
优惠之道极难。未知何以则可也。窃尝妄料。齐民之于军丁。其多寡不啻相万。而终年安坐。不输一钱。彼军丁独贤之怨。于是转甚矣。若通计一国之男口。毋论大小贵贱。人出若干米斗。名曰军食。岁给军丁五六斛。使之优其衣食。资其弓马。在家而绝官家诛求之苦。出外而无妻子冻馁之念。庶足为优惠之一道耳。 祖宗朝给保之法。至矣尽矣。而累经兵乱。死亡殆尽。每户单丁。而其有一保者亦鲜矣。自今以后。申明此制。每户俱三保。分番递上。相助其力。而减入番之日数。则似无废农之患矣。兵水营各镇浦。既有主将。且有军官及带率下人。固不可无食而供职。则其日用供亿之费。似当有定给之规矣。继自今制其常用。丰其廪食。或画给以其地岁入之税。或分定于旁邑。而毋复使侵掠军卒。其除防差备。亦令递番轮回。以宽其力。则军情胥悦。而边鄙克固矣。当今守西之卒。岁更之数。殆且数万。分防诸处。浮寄孤悬。行者有契阔怨旷之叹。居者有赍送馈饷之劳。次第调发。每岁不已。观此形势。曾无一贼犯境之虞而国内罢矣。若不及今改图则后悔无及。臣闻江边列邑。皆有土兵。精锐颇多。其馀丁壮。亦且不少。今若悉罢下三道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26H 页
 之兵。收布入送。召募土兵。优给米布。以代南兵则与贼接壤。谙其形便。与南兵之心畏胡者。甚相悬矣。而亦且减南兵远戍之苦。此所谓一举而两得者也。顷者一二臣僚。有以此事陈达者。 朝廷欲采而用之。其后无闻焉。伏愿 圣明特下此议。详确而施行之。不胜幸甚。何谓严禁卫。平时内禁卫,兼司仆,羽林卫。号为禁军者。皆是一等武士也。至如别侍卫,定虏卫,甲士。无非能射之人。正兵及杂色军之入卫禁中者。无非精锐。其为周防戒备之意。可谓密矣。所谓别侍卫者。 光庙朝庚辰之年。武科出身之数。多至八百。不可尽除武职。故设卫而属之。以壮禁卫。今者前后武科出身之数。至于数万。不解操弓。而代射冒科者甚多。以此宿卫。何补于缓急乎。伏愿 殿下特令兵曹。别试其才。设卫而属之。其馀。分番赴西。则人皆乐属。禁卫自壮矣。今以四大将军官。轮番入直。此乃一时权宜之策。在渠则有祈父不聪之怨。在国则有廪料难继之患。事定时平则一时刱立之规。不可仍存。然一朝遽然罢遣。亦似难便。须令兵曹择其尤者。边将有窠则以此填差。以酬其劳。其馀诸色禁卫。亦加鍊试之法。等第其禄。而为之激劝。至于都监三手。亦
之兵。收布入送。召募土兵。优给米布。以代南兵则与贼接壤。谙其形便。与南兵之心畏胡者。甚相悬矣。而亦且减南兵远戍之苦。此所谓一举而两得者也。顷者一二臣僚。有以此事陈达者。 朝廷欲采而用之。其后无闻焉。伏愿 圣明特下此议。详确而施行之。不胜幸甚。何谓严禁卫。平时内禁卫,兼司仆,羽林卫。号为禁军者。皆是一等武士也。至如别侍卫,定虏卫,甲士。无非能射之人。正兵及杂色军之入卫禁中者。无非精锐。其为周防戒备之意。可谓密矣。所谓别侍卫者。 光庙朝庚辰之年。武科出身之数。多至八百。不可尽除武职。故设卫而属之。以壮禁卫。今者前后武科出身之数。至于数万。不解操弓。而代射冒科者甚多。以此宿卫。何补于缓急乎。伏愿 殿下特令兵曹。别试其才。设卫而属之。其馀。分番赴西。则人皆乐属。禁卫自壮矣。今以四大将军官。轮番入直。此乃一时权宜之策。在渠则有祈父不聪之怨。在国则有廪料难继之患。事定时平则一时刱立之规。不可仍存。然一朝遽然罢遣。亦似难便。须令兵曹择其尤者。边将有窠则以此填差。以酬其劳。其馀诸色禁卫。亦加鍊试之法。等第其禄。而为之激劝。至于都监三手。亦沙溪先生遗稿卷一 第 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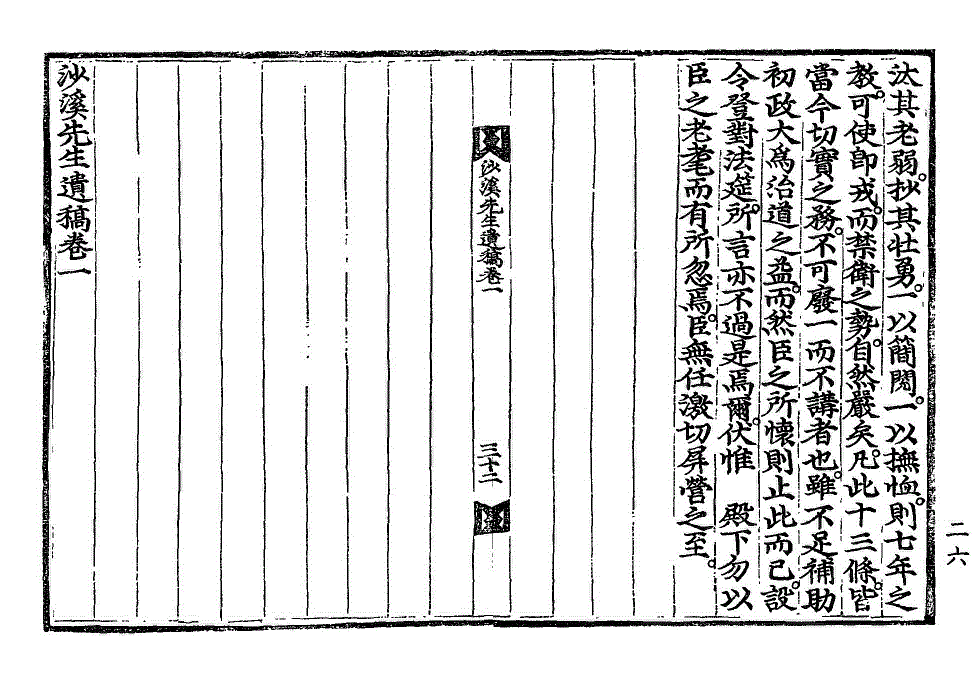 汰其老弱。抄其壮勇。一以简阅。一以抚恤。则七年之教。可使即戎。而禁卫之势。自然严矣。凡此十三条。皆当今切实之务。不可废一而不讲者也。虽不足补助初政大为治道之益。而然臣之所怀则止此而已。设令登对法筵。所言亦不过是焉尔。伏惟 殿下勿以臣之老耄而有所忽焉。臣无任激切屏营之至。
汰其老弱。抄其壮勇。一以简阅。一以抚恤。则七年之教。可使即戎。而禁卫之势。自然严矣。凡此十三条。皆当今切实之务。不可废一而不讲者也。虽不足补助初政大为治道之益。而然臣之所怀则止此而已。设令登对法筵。所言亦不过是焉尔。伏惟 殿下勿以臣之老耄而有所忽焉。臣无任激切屏营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