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x 页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杂著○读史蠡测
[读史蠡测序]
余读宋史。往往见其是非瞀乱。去取不明。意见所及。未免随事有言。以示儿辈。题曰读史蠡测。
杂著○读史蠡测
[读史蠡测序]
余读宋史。往往见其是非瞀乱。去取不明。意见所及。未免随事有言。以示儿辈。题曰读史蠡测。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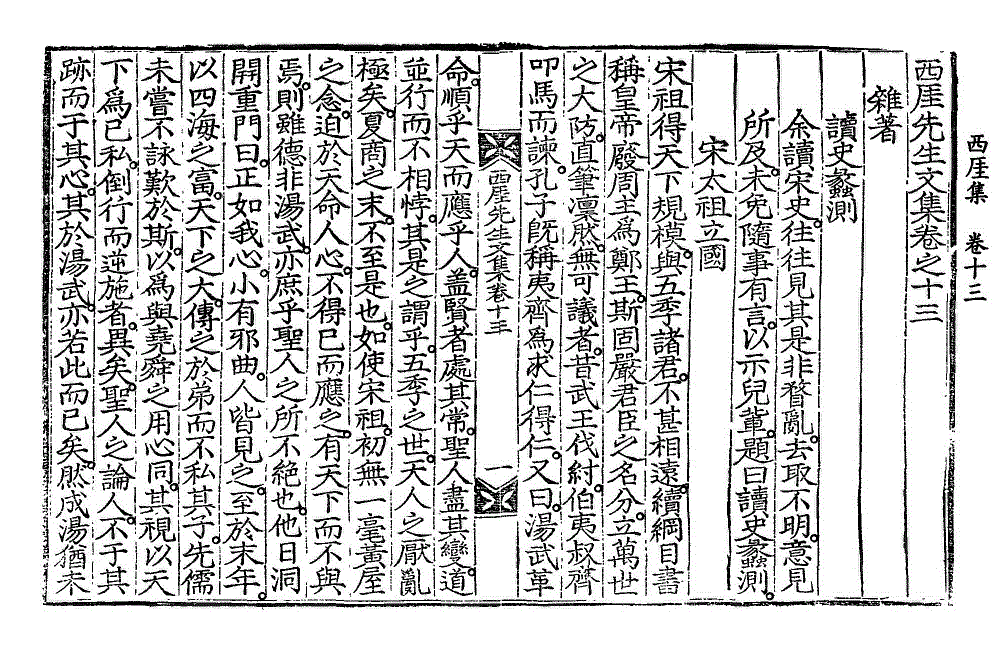 宋太祖立国
宋太祖立国宋祖得天下规模。与五季诸君。不甚相远。续纲目书称皇帝废周主为郑王。斯固严君臣之名分。立万世之大防。直笔凛然。无可议者。昔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孔子既称夷齐为求仁得仁。又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盖贤者处其常。圣人尽其变。道并行而不相悖。其是之谓乎。五季之世。天人之厌乱极矣。夏商之末。不至是也。如使宋祖。初无一毫黄屋之念。迫于天命人心。不得已而应之。有天下而不与焉。则虽德非汤武。亦庶乎圣人之所不绝也。他日洞开重门曰。正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见之。至于末年。以四海之富。天下之大。传之于弟而不私其子。先儒未尝不咏叹于斯。以为与尧舜之用心同。其视以天下为己私。倒行而逆施者。异矣。圣人之论人。不于其迹而于其心。其于汤武。亦若此而已矣。然成汤犹未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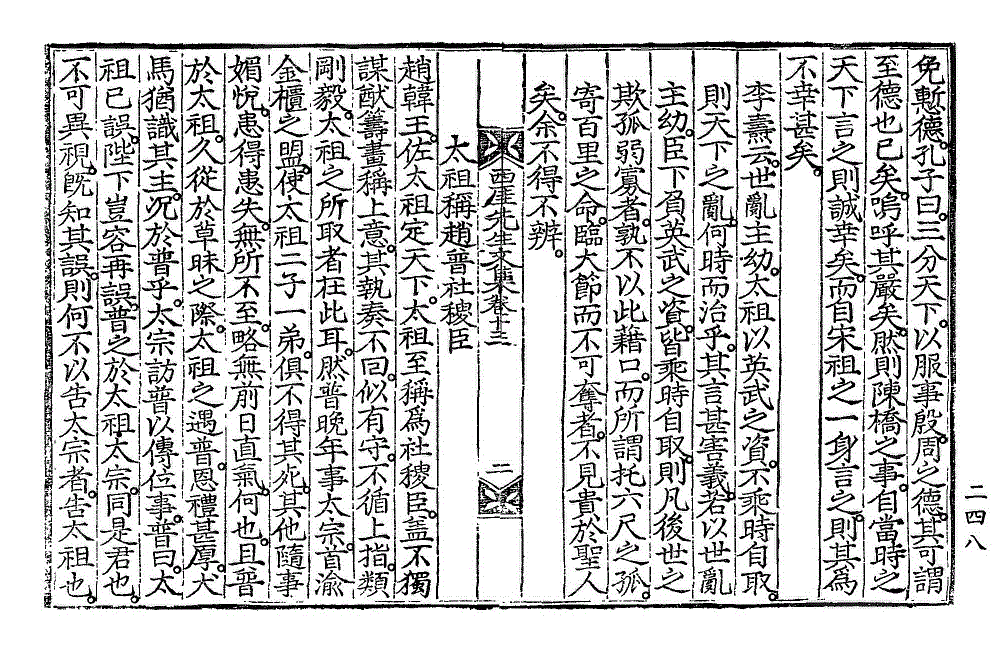 免惭德。孔子曰。三分天下。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呜呼其严矣。然则陈桥之事。自当时之天下言之则诚幸矣。而自宋祖之一身言之。则其为不幸甚矣。
免惭德。孔子曰。三分天下。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呜呼其严矣。然则陈桥之事。自当时之天下言之则诚幸矣。而自宋祖之一身言之。则其为不幸甚矣。李焘云。世乱主幼。太祖以英武之资。不乘时自取。则天下之乱。何时而治乎。其言甚害义。若以世乱主幼。臣下负英武之资。皆乘时自取。则凡后世之欺孤弱寡者。孰不以此藉口。而所谓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者。不见贵于圣人矣。余不得不辨。
太祖称赵普社稷臣
赵韩王。佐太祖定天下。太祖至称为社稷臣。盖不独谋猷筹画称上意。其执奏不回。似有守。不循上指。类刚毅。太祖之所取者在此耳。然普晚年事太宗。首渝金匮之盟。使太祖二子一弟。俱不得其死。其他随事媚悦。患得患失。无所不至。略无前日直气。何也。且普于太祖。久从于草昧之际。太祖之遇普。恩礼甚厚。犬马犹识其主。况于普乎。太宗访普以传位事。普曰。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普之于太祖,太宗。同是君也。不可异视。既知其误。则何不以告太宗者。告太祖也。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49H 页
 父有天下。传之子。周,汉以来。未易此道。非必私厚其子。亦止乱之道也。汉景帝曲循太后之意。欲传位梁王。詹事窦婴引卮酒进曰。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上何以得传梁王。其议遂格。太后虽不悦。无如之何。汉室之不乱。婴之力也。当杜太后临崩。遗命兄弟相传。其意亦主于国有长君。为天下长久计。太祖之受命不辞者。尧舜之心也。普以大臣。适在其侧。亲与其事。一言救正。正是其责。默然承受。又从而赞成之。何意也。奸人之心。善于附会。惟利是从。利在君上则从君上。利在宫闱则从宫闱。利在外庭则从外庭。利在公论则从公论。视人之眉睫向背。而低䀚万变。不可方物。此辨之所以难也。太祖友爱至深。常谓晋王龙行虎步。太平天子。传位之定。久矣。普知其如此。故既成金匮之盟。以顺太祖之意。又以邀后福于太宗。及太宗立。其施为意向。非复前日太祖之心。而德昭,德芳等。以谴相继殒殁。于是。普鼠拱私室。潜伺密覵。知其身之奇货。正在于构陷廷美。以中太宗之欲。故攘臂为之。不复顾念太祖平昔之恩。又不顾太后要质鬼神之约。何其忍哉。而其源不过患得 念致之也。然则前日事太祖。謇然有直臣之节者。非真有直节。亦以
父有天下。传之子。周,汉以来。未易此道。非必私厚其子。亦止乱之道也。汉景帝曲循太后之意。欲传位梁王。詹事窦婴引卮酒进曰。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上何以得传梁王。其议遂格。太后虽不悦。无如之何。汉室之不乱。婴之力也。当杜太后临崩。遗命兄弟相传。其意亦主于国有长君。为天下长久计。太祖之受命不辞者。尧舜之心也。普以大臣。适在其侧。亲与其事。一言救正。正是其责。默然承受。又从而赞成之。何意也。奸人之心。善于附会。惟利是从。利在君上则从君上。利在宫闱则从宫闱。利在外庭则从外庭。利在公论则从公论。视人之眉睫向背。而低䀚万变。不可方物。此辨之所以难也。太祖友爱至深。常谓晋王龙行虎步。太平天子。传位之定。久矣。普知其如此。故既成金匮之盟。以顺太祖之意。又以邀后福于太宗。及太宗立。其施为意向。非复前日太祖之心。而德昭,德芳等。以谴相继殒殁。于是。普鼠拱私室。潜伺密覵。知其身之奇货。正在于构陷廷美。以中太宗之欲。故攘臂为之。不复顾念太祖平昔之恩。又不顾太后要质鬼神之约。何其忍哉。而其源不过患得 念致之也。然则前日事太祖。謇然有直臣之节者。非真有直节。亦以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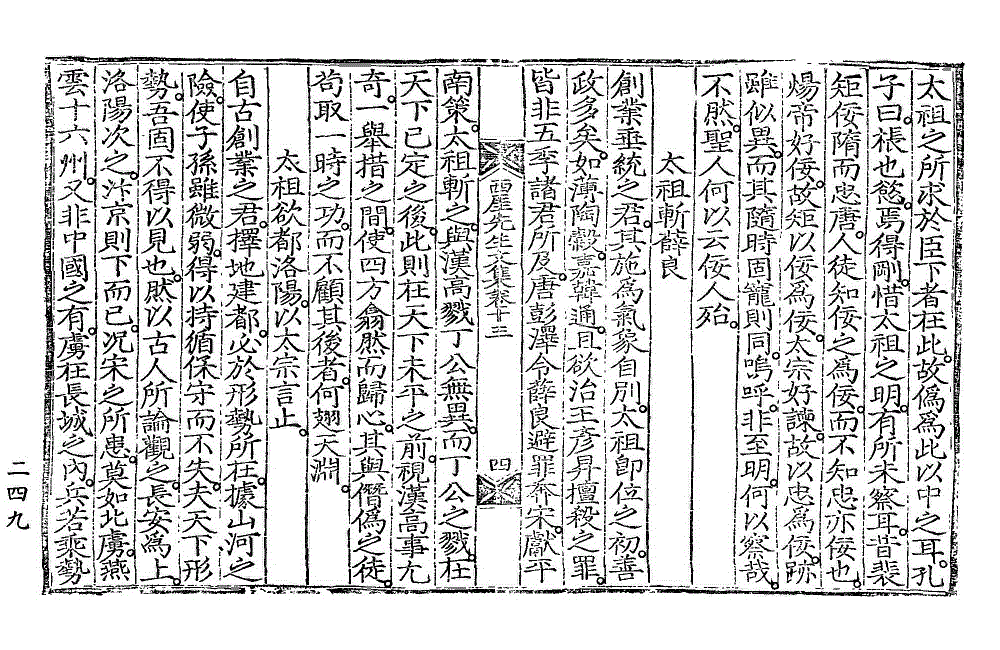 太祖之所求于臣下者在此。故伪为此以中之耳。孔子曰。枨也欲。焉得刚。惜太祖之明。有所未察耳。昔裴矩佞隋而忠唐。人徒知佞之为佞。而不知忠亦佞也。炀帝好佞。故矩以佞为佞。太宗好谏。故以忠为佞。迹虽似异。而其随时固宠则同。呜呼。非至明。何以察哉。不然。圣人何以云佞人殆。
太祖之所求于臣下者在此。故伪为此以中之耳。孔子曰。枨也欲。焉得刚。惜太祖之明。有所未察耳。昔裴矩佞隋而忠唐。人徒知佞之为佞。而不知忠亦佞也。炀帝好佞。故矩以佞为佞。太宗好谏。故以忠为佞。迹虽似异。而其随时固宠则同。呜呼。非至明。何以察哉。不然。圣人何以云佞人殆。太祖斩薛良
创业垂统之君。其施为气象自别。太祖即位之初。善政多矣。如薄陶谷。嘉韩通。且欲治王彦升擅杀之罪。皆非五季诸君所及。唐彭泽令薛良避罪奔宋。献平南策。太祖斩之。与汉高戮丁公无异。而丁公之戮。在天下已定之后。此则在天下未平之前。视汉高事尤奇。一举措之间。使四方翕然而归心。其与僭伪之徒。苟取一时之功。而不顾其后者。何翅天渊。
太祖欲都洛阳。以太宗言止。
自古创业之君。择地建都。必于形势所在。据山河之险。使子孙虽微弱。得以持循保守而不失。夫天下形势。吾固不得以见也。然以古人所论观之。长安为上。洛阳次之。汴京则下而已。况宋之所患。莫如北虏。燕云十六州。又非中国之有。虏在长城之内。兵若乘势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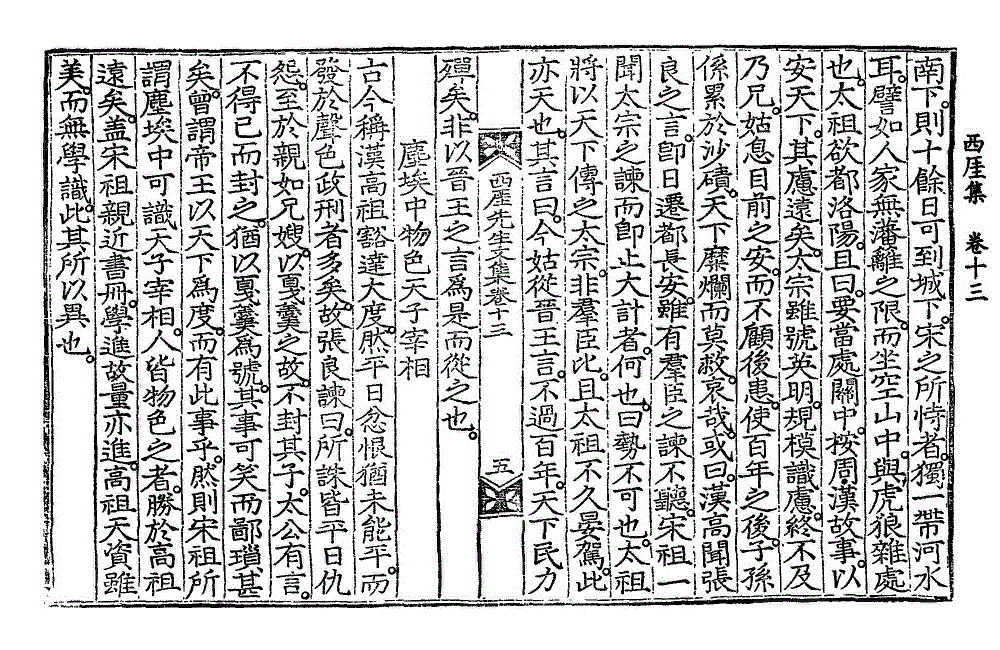 南下。则十馀日可到城下。宋之所恃者。独一带河水耳。譬如人家无藩篱之限。而坐空山中。与虎狼杂处也。太祖欲都洛阳。且曰。要当处关中。按周,汉故事。以安天下。其虑远矣。太宗虽号英明。规模识虑。终不及乃兄。姑息目前之安。而不顾后患。使百年之后。子孙系累于沙碛。天下糜烂而莫救。哀哉。或曰。汉高闻张良之言。即日迁都长安。虽有群臣之谏不听。宋祖一闻太宗之谏而即止大计者。何也。曰势不可也。太祖将以天下传之太宗。非群臣比。且太祖不久晏驾。此亦天也。其言曰。今姑从晋王言。不过百年。天下民力殚矣。非以晋王之言为是而从之也。
南下。则十馀日可到城下。宋之所恃者。独一带河水耳。譬如人家无藩篱之限。而坐空山中。与虎狼杂处也。太祖欲都洛阳。且曰。要当处关中。按周,汉故事。以安天下。其虑远矣。太宗虽号英明。规模识虑。终不及乃兄。姑息目前之安。而不顾后患。使百年之后。子孙系累于沙碛。天下糜烂而莫救。哀哉。或曰。汉高闻张良之言。即日迁都长安。虽有群臣之谏不听。宋祖一闻太宗之谏而即止大计者。何也。曰势不可也。太祖将以天下传之太宗。非群臣比。且太祖不久晏驾。此亦天也。其言曰。今姑从晋王言。不过百年。天下民力殚矣。非以晋王之言为是而从之也。尘埃中物色天子宰相
古今称汉高祖豁达大度。然平日忿恨犹未能平。而发于声色政刑者多矣。故张良谏曰。所诛皆平日仇怨。至于亲如兄嫂。以戛羹之故。不封其子。太公有言。不得已而封之。犹以戛羹为号。其事可笑而鄙琐甚矣。曾谓帝王以天下为度。而有此事乎。然则宋祖所谓尘埃中可识天子宰相。人皆物色之者。胜于高祖远矣。盖宋祖亲近书册。学进故量亦进。高祖天资虽美。而无学识。此其所以异也。
太祖崩
烛影之事。天下之大变。亦古今之大疑也。琼山丘氏独以为不可信。辨之甚详。(见世史正纲)然所引小说。亦近于语怪。不足以破千古之惑。大抵事之虚实。虽不可知。而观太宗后日所以待太祖者甚悖。传言兵莫憯于志。莫铘为下。春秋之法。原情定罪。太宗虽被首恶之名。庸何辞焉。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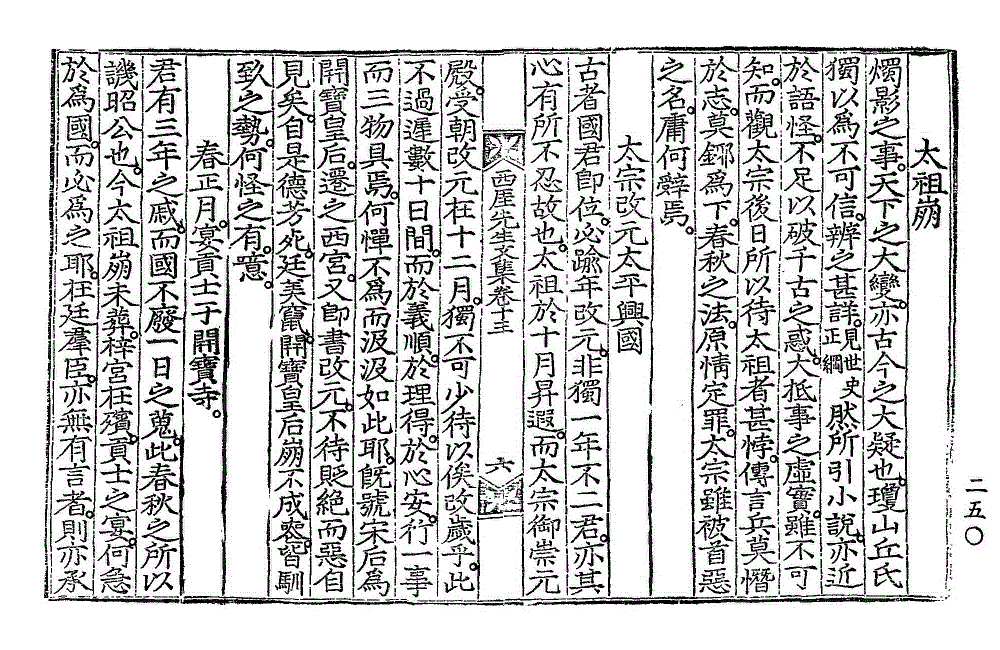 太宗改元太平兴国
太宗改元太平兴国古者国君即位。必踰年改元。非独一年不二君。亦其心有所不忍故也。太祖于十月升遐。而太宗御崇元殿。受朝改元在十二月。独不可少待以俟改岁乎。此不过迟数十日间。而于义顺。于理得。于心安。行一事而三物具焉。何惮不为而汲汲如此耶。既号宋后为开宝皇后。迁之西宫。又即书改元。不待贬绝而恶自见矣。自是德芳死。廷美窜。开宝皇后崩不成丧。皆驯致之势。何怪之有。噫。
春正月。宴贡士于开宝寺。
君有三年之戚。而国不废一日之蒐。此春秋之所以讥昭公也。今太祖崩未葬。梓宫在殡。贡士之宴。何急于为国。而必为之耶。在廷群臣。亦无有言者。则亦承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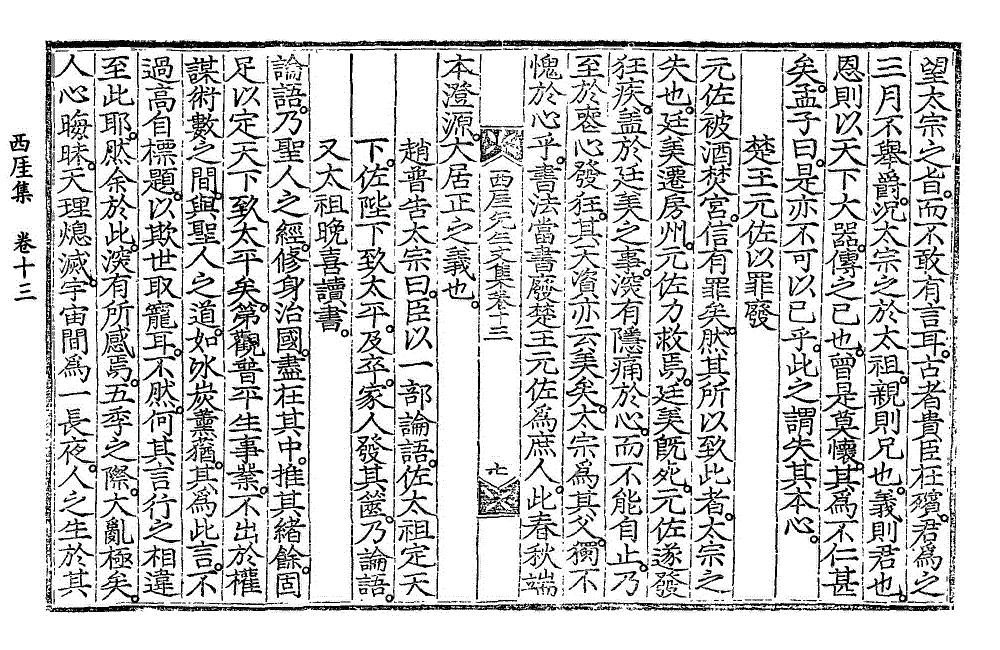 望太宗之旨。而不敢有言耳。古者贵臣在殡。君为之三月不举爵。况太宗之于太祖。亲则兄也。义则君也。恩则以天下大器。传之己也。曾是莫怀。其为不仁甚矣。孟子曰。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望太宗之旨。而不敢有言耳。古者贵臣在殡。君为之三月不举爵。况太宗之于太祖。亲则兄也。义则君也。恩则以天下大器。传之己也。曾是莫怀。其为不仁甚矣。孟子曰。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楚王元佐以罪废
元佐被酒焚宫。信有罪矣。然其所以致此者。太宗之失也。廷美迁房州。元佐力救焉。廷美既死。元佐遂发狂疾。盖于廷美之事。深有隐痛于心。而不能自止。乃至于丧心发狂。其天资亦云美矣。太宗为其父。独不愧于心乎。书法当书废楚王元佐为庶人。此春秋端本澄源。大居正之义也。
赵普告太宗曰。臣以一部论语。佐太祖定天下。佐陛下致太平。及卒。家人发其箧。乃论语。又太祖晚喜读书。
论语。乃圣人之经。修身治国。尽在其中。推其绪馀。固足以定天下致太平矣。第观普平生事业。不出于权谋术数之间。与圣人之道。如冰炭薰莸。其为此言。不过高自标题。以欺世取宠耳。不然。何其言行之相违至此耶。然余于此。深有所感焉。五季之际。大乱极矣。人心晦昧。天理熄灭。宇宙间为一长夜。人之生于其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1L 页
 时者。惟群群逐逐。奔走经营。以图富贵。则止耳。义理之见。诚无所发于其间。况普素以寡学闻。其视经术。不翅越人之于章甫耳。夏虫不可以语冰。井蛙不可以论海。朝夕倚市。贩卖求利者。不问农桑之业。何者。所念由于所习故也。普以功名。乘时奋迹。致位宰相。富贵已极。志已满矣。气已得矣。顾于晚年。子女声色之中。沈溺宴乐之馀。惕然反顾。知有所谓圣人之书者。而取之藏之箧笥。闭门而读诵之。又以是告诸君。正是粗人作细事。无论得与不得。只此一事。已为奇矣。汉,唐之初。萧,曹,房,杜号为贤相。未闻有此事。岂普之贤。胜于萧,曹,房,杜乎。物有其源。事有其兆。斯文之兴丧。世道之污隆。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础润而雨。月晕而风。物固有然者矣。而动于人心之微者。尤为明著。宋氏受命。天将佑启人文。使圣人之道。复明于天下。故精华兆朕。已露于立国之初。上观玄象而五星同晷。下察人事而人主与宰相。皆骎骎有向学之意。不待劝勉而自然如此。夫岂偶然哉。他日李文靖亦云。如论语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两句。尚不能行。圣人之言。终身诵之可也。自是儒术日盛。经学日广。一转而为湖学。再转而为伊,洛,关,闽。千有馀年圣
时者。惟群群逐逐。奔走经营。以图富贵。则止耳。义理之见。诚无所发于其间。况普素以寡学闻。其视经术。不翅越人之于章甫耳。夏虫不可以语冰。井蛙不可以论海。朝夕倚市。贩卖求利者。不问农桑之业。何者。所念由于所习故也。普以功名。乘时奋迹。致位宰相。富贵已极。志已满矣。气已得矣。顾于晚年。子女声色之中。沈溺宴乐之馀。惕然反顾。知有所谓圣人之书者。而取之藏之箧笥。闭门而读诵之。又以是告诸君。正是粗人作细事。无论得与不得。只此一事。已为奇矣。汉,唐之初。萧,曹,房,杜号为贤相。未闻有此事。岂普之贤。胜于萧,曹,房,杜乎。物有其源。事有其兆。斯文之兴丧。世道之污隆。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础润而雨。月晕而风。物固有然者矣。而动于人心之微者。尤为明著。宋氏受命。天将佑启人文。使圣人之道。复明于天下。故精华兆朕。已露于立国之初。上观玄象而五星同晷。下察人事而人主与宰相。皆骎骎有向学之意。不待劝勉而自然如此。夫岂偶然哉。他日李文靖亦云。如论语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两句。尚不能行。圣人之言。终身诵之可也。自是儒术日盛。经学日广。一转而为湖学。再转而为伊,洛,关,闽。千有馀年圣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2H 页
 学之不传者。一朝昭晰呈露。如日中天。呜呼盛矣。非天。其孰使之。孔子曰。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岂不信哉。
学之不传者。一朝昭晰呈露。如日中天。呜呼盛矣。非天。其孰使之。孔子曰。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岂不信哉。葬开宝皇后宋氏于永昌陵
于是开宝皇后之崩。已三年矣。太宗之情见矣。
引烛焚诏
美哉。李文靖之为臣也。能以直道事君。而不以承顺为恭。大哉。真宗之为君也。能容大臣之格非。而不留于宫妾之邪媚。率是道也。天下岂有不治。朝纲岂有不立。政事岂有不得其平者哉。语曰。为君难。为臣不易。然其难易。亦系乎世之治乱。盖乱世之为君易。治世之为君难。治世之为臣易。乱世之为臣难。治世之君。兢兢业业。发政处事。惟恐或有所失。舍己从人。闻谏弗咈。此其所以难也。乱世之君。肆意妄行。设刀锯斧钺。以待天下之人。高枕宠乐。而人莫敢忤其意。此所以易也。臣则不然。在治世则惟道义是行。而不忧其违忤。惟己志是守。而不求于苟合。身安而道全。泽流而名著。上不惧于触犯。下不罹于谗慝。岂不易乎。在乱世则劳心焦思而君不察其忠。竭诚尽节而上不然其信。群邪杂糅。左牵右掣。志不得行而身不得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2L 页
 保。小则系累于牢狱。重则流窜于岭海。所谓云不可仕。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仕。怨及朋友。羝羊触藩。进退维谷。可谓难矣。人君当先行其难。以责臣下之易。及其功成治定。天下无事。则君臣一心。上下同乐。安富尊荣。怡然于太和之域。同享其福而无复有难矣。昔汉太尉杨伯起忤一乳媪。绝命于城外。西汉王嘉一言董贤。下狱而死。呜呼。士之处乱世。岂非不幸之甚乎。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惟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者。免矣。
保。小则系累于牢狱。重则流窜于岭海。所谓云不可仕。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仕。怨及朋友。羝羊触藩。进退维谷。可谓难矣。人君当先行其难。以责臣下之易。及其功成治定。天下无事。则君臣一心。上下同乐。安富尊荣。怡然于太和之域。同享其福而无复有难矣。昔汉太尉杨伯起忤一乳媪。绝命于城外。西汉王嘉一言董贤。下狱而死。呜呼。士之处乱世。岂非不幸之甚乎。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惟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者。免矣。王旦云张师德两及其门。待我薄。
宰相以公心直道。秉匀于上。而百官承序于下。使之各治其职。视其能否而进退之。其进非私喜也。其退非私怒也。一出于公。而已无与焉。可也。彼小人者。不然。上则窥觇人主之好恶而先意逢迎。下则招纳嗜利。躁进之徒。日夜盈门。引入要路。以为爪牙羽翼。贤愚混淆。躁竞成风。治由是坏。政由是乱。盖士之逐名干进。如水趋下。堤防少解。末流难制。王文正不见张师德。李文靖不用新进喜事之人。前辈风流德业。可以想见。以此而息奔竞之路。杜侥倖之门。风俗安得不厚。士习安得不美。其辅佐太平。蔚然为一代宗臣。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3H 页
 不亦宜乎。或曰。然则周公下白屋。吐哺握发。非欤。曰周公之心。只在国事。罗天下之善。以成天下之务。当时之进见者。亦以周公之心为心。岂如后世阘茸斗筲之辈。昏夜乞哀。以迁一级得一官为心。而奔走于宰相之门哉。语云。恶紫。恐其乱朱也。又曰。是故。恶夫佞者。
不亦宜乎。或曰。然则周公下白屋。吐哺握发。非欤。曰周公之心。只在国事。罗天下之善。以成天下之务。当时之进见者。亦以周公之心为心。岂如后世阘茸斗筲之辈。昏夜乞哀。以迁一级得一官为心。而奔走于宰相之门哉。语云。恶紫。恐其乱朱也。又曰。是故。恶夫佞者。城下之盟。春秋小国所耻。
澶渊之役。宋人以为奇功。而王钦若独以城下之盟为辱。钦若固小人。其意不过借此以倾寇公。然其所言春秋所耻者。近乎。不近乎。当时既不能辨。后世又无论之者。何欤。曰。此名似而实非也。春秋之时。列国诸侯。位均体敌。其相会盟也。或以衣冠。或以兵车。或以朝聘。或以修睦。若兵入四境而不能御。造其国都而不能却。势穷力屈。匍匐乞怜。与盟于城门之外。仅免肉袒牵羊。天下笑之。斯固可耻之甚者。故曰宁以国毙。不能从也。澶渊之事则不然。虏主举国入寇。中外震骇。真宗亲御六飞。毅然出征。临境而止。在我有堂堂之势。虏乃畏威赧德。逡巡请盟而退。所谓发舒华夏之气。震惊毡裘之心。主客内外之势。迥然不同。不可以春秋之事为比也。如使其时无此举。从钦若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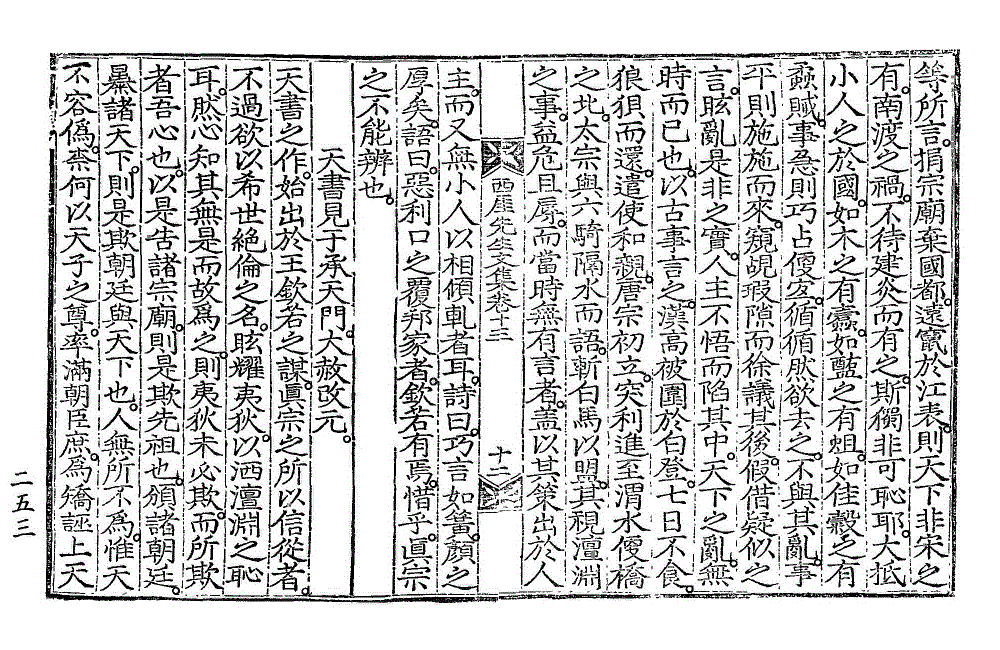 等所言。捐宗庙弃国都。远窜于江表。则天下非宋之有。南渡之祸。不待建炎而有之。斯独非可耻耶。大抵小人之于国。如木之有蠹。如醢之有蛆。如佳谷之有蟊贼。事急则巧占便宜。循循然欲去之。不与其乱。事平则施施而来。窥觇瑕隙而徐议其后。假借疑似之言。眩乱是非之实。人主不悟而陷其中。天下之乱。无时而已也。以古事言之。汉高被围于白登。七日不食。狼狈而还。遣使和亲。唐宗初立。突利进至渭水便桥之北。太宗与六骑隔水而语。斩白马以盟。其视澶渊之事。益危且辱。而当时无有言者。盖以其策出于人主。而又无小人以相倾轧者耳。诗曰。巧言如簧。颜之厚矣。语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钦若有焉。惜乎。真宗之不能辨也。
等所言。捐宗庙弃国都。远窜于江表。则天下非宋之有。南渡之祸。不待建炎而有之。斯独非可耻耶。大抵小人之于国。如木之有蠹。如醢之有蛆。如佳谷之有蟊贼。事急则巧占便宜。循循然欲去之。不与其乱。事平则施施而来。窥觇瑕隙而徐议其后。假借疑似之言。眩乱是非之实。人主不悟而陷其中。天下之乱。无时而已也。以古事言之。汉高被围于白登。七日不食。狼狈而还。遣使和亲。唐宗初立。突利进至渭水便桥之北。太宗与六骑隔水而语。斩白马以盟。其视澶渊之事。益危且辱。而当时无有言者。盖以其策出于人主。而又无小人以相倾轧者耳。诗曰。巧言如簧。颜之厚矣。语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钦若有焉。惜乎。真宗之不能辨也。天书见于承天门。大赦改元。
天书之作。始出于王钦若之谋。真宗之所以信从者。不过欲以希世绝伦之名。眩耀夷狄。以洒澶渊之耻耳。然心知其无是而故为之。则夷狄未必欺。而所欺者吾心也。以是告诸宗庙。则是欺先祖也。颁诸朝廷。暴诸天下。则是欺朝廷与天下也。人无所不为。惟天不容伪。柰何以天子之尊。率满朝臣庶。为矫诬上天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4H 页
 之举。而无所忌惮。岂非可怪之甚乎。昔秦皇,汉武求神仙。祷祀神祇多矣。然此则惑于方士之言。不知其无有而求之。罪在于不明。要不足深责。其视宋朝君臣明知其虚伪。相率而行之。其于伛偻磬折。登降荐献之际。何以为颜。亦何以为心耶。呜呼。小人之愚弄其君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之举。而无所忌惮。岂非可怪之甚乎。昔秦皇,汉武求神仙。祷祀神祇多矣。然此则惑于方士之言。不知其无有而求之。罪在于不明。要不足深责。其视宋朝君臣明知其虚伪。相率而行之。其于伛偻磬折。登降荐献之际。何以为颜。亦何以为心耶。呜呼。小人之愚弄其君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河图,洛书真有是耶。圣人以神道设教。
大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果何物。而圣人之则之也柰何。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一者诚。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圣人体天行道。亦真实无妄而已。如使河图洛书不出于天。则圣人必不假为是象。以欺天下与后世也。尝试论之。天地之间。理与气而已。理非气不形。气非理不生。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至百千万亿。莫非自然之象。自然之数也。仰而昭布于上者此也。俯而融结于下者此也。充塞两间。流行变化。飞潜动植。糟粕煨烬。无非此个物事。既有其理。不能无气。既有其气。不能无象。既有其象。不能无数。河图洛书之为物。亦若此而已。圣人之画卦。不但取象于河图。其取义甚广。故曰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若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4L 页
 如杜镐之说。则是皆本无是事。而出于圣人之假设耶。姑以人身言之。乾为首。坤为腹。离为目。坎为耳。兑为口。震为足。巽为手。艮为背。假使伏羲时无河图。八卦亦可画。毕竟先有此象而圣人取之。不成说圣人欲设教而假设此象也。又徒知河图洛书为神怪不测。而不知神怪不测者。近在于吾身。试问人之一身。目何为而视。耳何为而听。口何为而言。鼻何为而嗅。手足何为而能运动。此之不怪。而独怪其图书之数与象。以为不出于天。而出于圣人之手。宁不可哂乎。吾意杜镐者。亦王氏之孚也。其为此言。必先受钦若风旨。傅会其事。以中真宗之意。不然。何以舍大传明白之训。而为此漫浪无据之语耶。当时厚德重望。难动以非义如王文正。犹被钦若笼络。况书生多欲少刚如杜氏子者。特发蒙耳。史言不测帝意。谩应曰云云。吾笑之不独当时君臣为所欺。作史者。亦为钦若所欺而不自悟也。
如杜镐之说。则是皆本无是事。而出于圣人之假设耶。姑以人身言之。乾为首。坤为腹。离为目。坎为耳。兑为口。震为足。巽为手。艮为背。假使伏羲时无河图。八卦亦可画。毕竟先有此象而圣人取之。不成说圣人欲设教而假设此象也。又徒知河图洛书为神怪不测。而不知神怪不测者。近在于吾身。试问人之一身。目何为而视。耳何为而听。口何为而言。鼻何为而嗅。手足何为而能运动。此之不怪。而独怪其图书之数与象。以为不出于天。而出于圣人之手。宁不可哂乎。吾意杜镐者。亦王氏之孚也。其为此言。必先受钦若风旨。傅会其事。以中真宗之意。不然。何以舍大传明白之训。而为此漫浪无据之语耶。当时厚德重望。难动以非义如王文正。犹被钦若笼络。况书生多欲少刚如杜氏子者。特发蒙耳。史言不测帝意。谩应曰云云。吾笑之不独当时君臣为所欺。作史者。亦为钦若所欺而不自悟也。契丹主为真宗举哀
自古南北交欢。亦多矣。然其岁久而情至。未有如契丹之与宋也。观契丹主为真宗举哀发丧。后妃以下。皆为沾涕伤悼之甚。不啻如亲兄弟。亦异事。而前后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5H 页
 所未闻也。自是子孙相承。百有馀年。信使往来。边门无犬吠之警。一朝契丹为女真所困。宋既不能救。方且潜遣间使。越海相约。与之夹攻。渝盟负信。中国反不如夷狄。其不旋踵而身遭系累之辱。岂无天道耶。譬如盗入邻家。不能救。反与之分其财。当时已有此语而不悟。呜呼。宣和君臣。真穿窬之类。其及也宜矣。圣人云忠信笃敬。可行于蛮貊。不然则难乎免矣。
所未闻也。自是子孙相承。百有馀年。信使往来。边门无犬吠之警。一朝契丹为女真所困。宋既不能救。方且潜遣间使。越海相约。与之夹攻。渝盟负信。中国反不如夷狄。其不旋踵而身遭系累之辱。岂无天道耶。譬如盗入邻家。不能救。反与之分其财。当时已有此语而不悟。呜呼。宣和君臣。真穿窬之类。其及也宜矣。圣人云忠信笃敬。可行于蛮貊。不然则难乎免矣。欧阳子朋党论
朋党。固难辨乎。曰。难辨则难辨。易辨则易辨。其难其易。只由于人主心术明暗之如何耳。曰。然则其辨之之道。可得闻乎。曰。朋党二字。虽曰相似。然君子有朋而无党。小人有党而无朋。盖朋者公也。党者私也。若不分其孰为朋孰为党。孰为公孰为私。而泛然以朋党目之。则形迹疑似之间。方且眩乱惶惑之不暇。而君子小人。终不可辨矣。孔子论君子小人。每于周比和同骄泰之属。对举而比论之。欲其就同中而知其有异。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夫朋者。同类之称。党者。相助匿非之名。二者之分。虽曰相近。而其实百千万里之远也。君子之所重者道义。同声则相应。同气则相求。所尚一出于公与正。谓之朋则可。谓之党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5L 页
 则不可。小人则不然。潝潝然相和。皋皋然相比。趋附款厚。不舍昼夜。意所好者。䨓同称誉。意所忌者。共相排摈。参知然后动。谋议然后言。虽欲自盖其私邪之迹。而观其所成就。不出于富贵势利之间。古人云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斯固善喻也。然其情态甚多。非可以一言尽也。尝试观之。君子之朋如比玉。温乎其相亲。而栗然而自守。小人之党如聚沙。始焉杂沓而不择精粗。终焉利尽则释然而相离。君子之朋如松柏。皆挺立独列而不相倚挨。然雨露之润。苍然蔚然而其色同也。风霜之下。不改柯易叶而其节同也。松柏不自以为同。而人之视之者。指以为类。若夫藤萝则蔓密蔽覆。非附物。不能自立。乔木在近则从乔木。荆棘在近则从荆棘。百结千回。无处而不相连络。其下隐暗。莫测深浅。而狐狸居焉。虫蛇宅焉。众恶归藏。观此数段。而朋党之情自分。斯固有目者皆可见。尚何难辨之有哉。惟小人。先结君心而与之为一。故始为所蔽而谓不可辨耳。世苟有大人君子欲去朋党之祸。无他道也。惟当先致力于格君心之非。使君心虚明公溥。无所蔽惑。则天下之表准既立。朝廷百官。悉归于正。而朋党之祸不作矣。不然而
则不可。小人则不然。潝潝然相和。皋皋然相比。趋附款厚。不舍昼夜。意所好者。䨓同称誉。意所忌者。共相排摈。参知然后动。谋议然后言。虽欲自盖其私邪之迹。而观其所成就。不出于富贵势利之间。古人云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斯固善喻也。然其情态甚多。非可以一言尽也。尝试观之。君子之朋如比玉。温乎其相亲。而栗然而自守。小人之党如聚沙。始焉杂沓而不择精粗。终焉利尽则释然而相离。君子之朋如松柏。皆挺立独列而不相倚挨。然雨露之润。苍然蔚然而其色同也。风霜之下。不改柯易叶而其节同也。松柏不自以为同。而人之视之者。指以为类。若夫藤萝则蔓密蔽覆。非附物。不能自立。乔木在近则从乔木。荆棘在近则从荆棘。百结千回。无处而不相连络。其下隐暗。莫测深浅。而狐狸居焉。虫蛇宅焉。众恶归藏。观此数段。而朋党之情自分。斯固有目者皆可见。尚何难辨之有哉。惟小人。先结君心而与之为一。故始为所蔽而谓不可辨耳。世苟有大人君子欲去朋党之祸。无他道也。惟当先致力于格君心之非。使君心虚明公溥。无所蔽惑。则天下之表准既立。朝廷百官。悉归于正。而朋党之祸不作矣。不然而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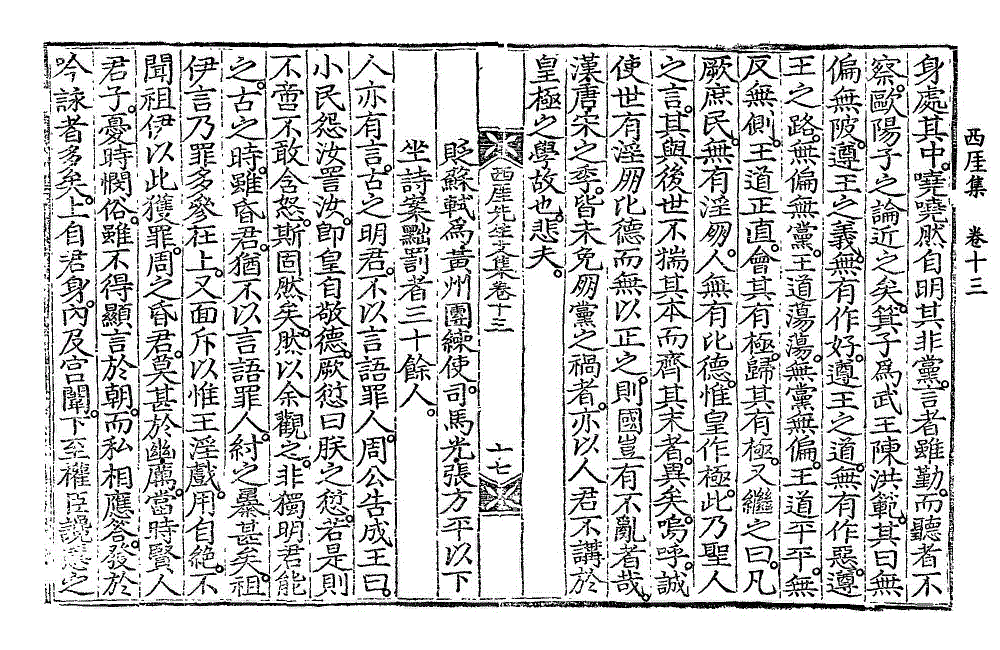 身处其中。哓哓然自明其非党。言者虽勤。而听者不察。欧阳子之论近之矣。箕子为武王陈洪范。其曰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又继之曰。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此乃圣人之言。其与后世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者。异矣。呜呼。诚使世有淫朋比德而无以正之。则国岂有不乱者哉。汉,唐,宋之季。皆未免朋党之祸者。亦以人君不讲于皇极之学故也。悲夫。
身处其中。哓哓然自明其非党。言者虽勤。而听者不察。欧阳子之论近之矣。箕子为武王陈洪范。其曰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又继之曰。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此乃圣人之言。其与后世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者。异矣。呜呼。诚使世有淫朋比德而无以正之。则国岂有不乱者哉。汉,唐,宋之季。皆未免朋党之祸者。亦以人君不讲于皇极之学故也。悲夫。贬苏轼为黄州团练使。司马光,张方平以下坐诗案黜罚者三十馀人。
人亦有言。古之明君。不以言语罪人。周公告成王曰。小民怨汝詈汝。即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若是则不啻不敢含怒。斯固然矣。然以余观之。非独明君能之。古之时。虽昏君。犹不以言语罪人。纣之暴甚矣。祖伊言乃罪多参在上。又面斥以惟王淫戏。用自绝。不闻祖伊以此获罪。周之昏君。莫甚于幽,厉。当时贤人君子。忧时悯俗。虽不得显言于朝。而私相应答。发于吟咏者多矣。上自君身。内及宫闱。下至权臣谗慝之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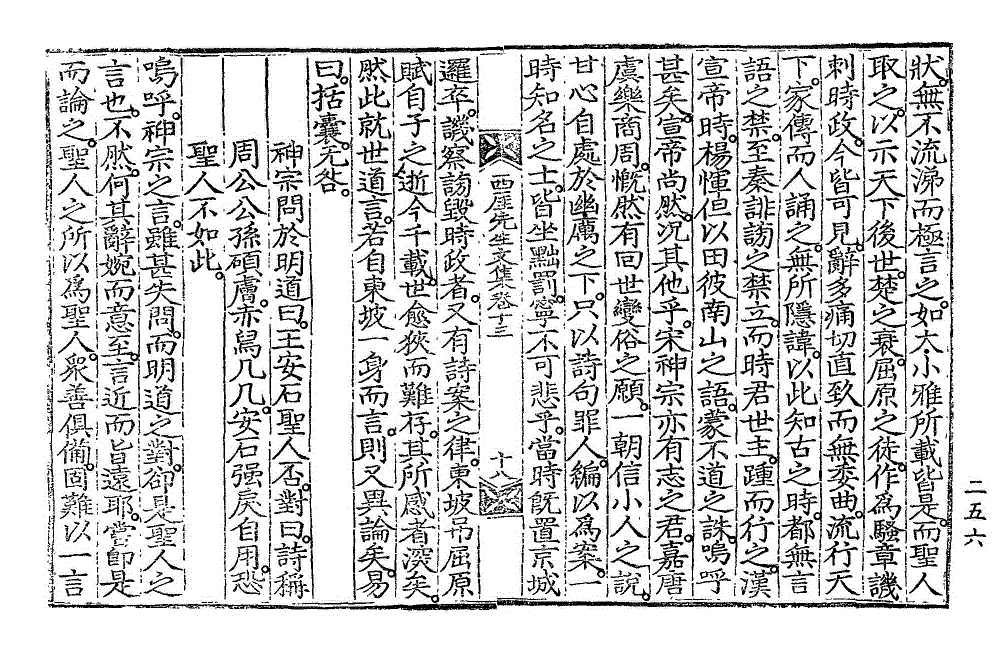 状。无不流涕而极言之。如大,小雅所载皆是。而圣人取之。以示天下后世。楚之衰。屈原之徒。作为骚章讥刺时政。今皆可见。辞多痛切直致而无委曲。流行天下。家传而人诵之。无所隐讳。以此知古之时。都无言语之禁。至秦诽谤之禁立。而时君世主。踵而行之。汉宣帝时。杨恽但以田彼南山之语。蒙不道之诛。呜呼甚矣。宣帝尚然。况其他乎。宋神宗亦有志之君。嘉唐虞乐商周。慨然有回世变俗之愿。一朝信小人之说。甘心自处于幽,厉之下。只以诗句罪人。编以为案。一时知名之士。皆坐黜罚。宁不可悲乎。当时既置京城逻卒。讥察谤毁时政者。又有诗案之律。东坡吊屈原赋自子之逝今千载。世愈狭而难存。其所感者深矣。然此就世道言。若自东坡一身而言。则又异论矣。易曰。括囊。无咎。
状。无不流涕而极言之。如大,小雅所载皆是。而圣人取之。以示天下后世。楚之衰。屈原之徒。作为骚章讥刺时政。今皆可见。辞多痛切直致而无委曲。流行天下。家传而人诵之。无所隐讳。以此知古之时。都无言语之禁。至秦诽谤之禁立。而时君世主。踵而行之。汉宣帝时。杨恽但以田彼南山之语。蒙不道之诛。呜呼甚矣。宣帝尚然。况其他乎。宋神宗亦有志之君。嘉唐虞乐商周。慨然有回世变俗之愿。一朝信小人之说。甘心自处于幽,厉之下。只以诗句罪人。编以为案。一时知名之士。皆坐黜罚。宁不可悲乎。当时既置京城逻卒。讥察谤毁时政者。又有诗案之律。东坡吊屈原赋自子之逝今千载。世愈狭而难存。其所感者深矣。然此就世道言。若自东坡一身而言。则又异论矣。易曰。括囊。无咎。神宗问于明道曰。王安石圣人否。对曰。诗称周公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安石强戾自用。恐圣人不如此。
呜呼。神宗之言。虽甚失问。而明道之对。却是圣人之言也。不然。何其辞婉而意至。言近而旨远耶。尝即是而论之。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众善俱备。固难以一言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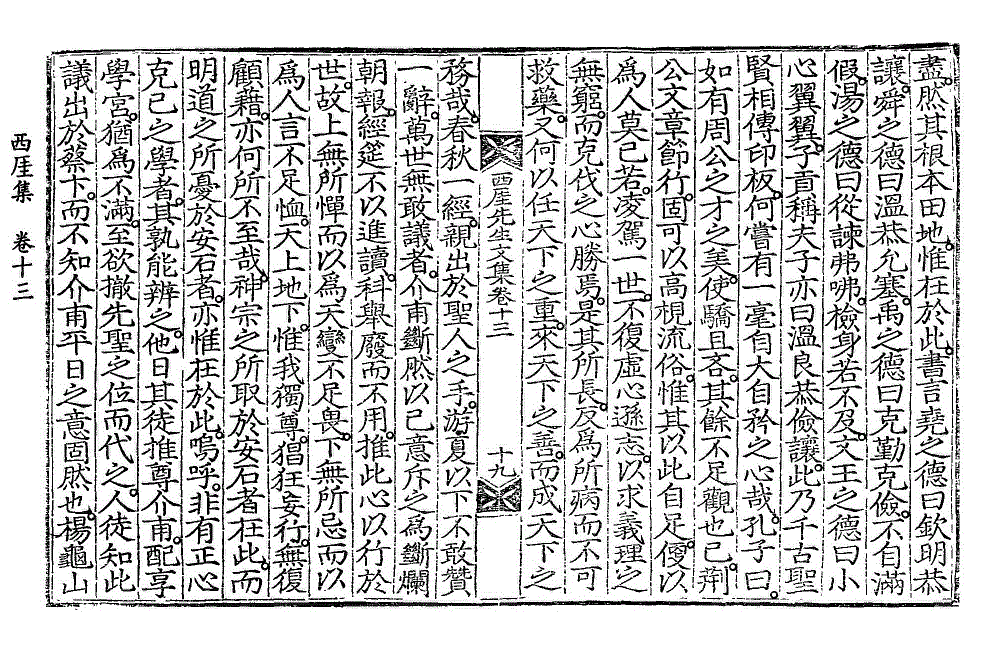 尽。然其根本田地。惟在于此。书言尧之德曰钦明恭让。舜之德曰温恭允塞。禹之德曰克勤克俭。不自满假。汤之德曰从谏弗咈。检身若不及。文王之德曰小心翼翼。子贡称夫子亦曰温良恭俭让。此乃千古圣贤相传印板。何尝有一毫自大自矜之心哉。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已。荆公文章节行。固可以高视流俗。惟其以此自足。便以为人莫己若。凌驾一世。不复虚心逊志。以求义理之无穷。而克伐之心胜焉。是其所长。反为所病而不可救药。又何以任天下之重。来天下之善。而成天下之务哉。春秋一经。亲出于圣人之手。游,夏以下不敢赞一辞。万世无敢议者。介甫断然以己意斥之为断烂朝报。经筵不以进读。科举废而不用。推此心以行于世。故上无所惮而以为天变不足畏。下无所忌而以为人言不足恤。天上地下。惟我独尊。猖狂妄行。无复顾藉。亦何所不至哉。神宗之所取于安石者在此。而明道之所忧于安石者。亦惟在于此。呜呼。非有正心克己之学者。其孰能辨之。他日其徒推尊介甫。配享学宫。犹为不满。至欲撤先圣之位而代之。人徒知此议出于蔡卞。而不知介甫平日之意固然也。杨龟山
尽。然其根本田地。惟在于此。书言尧之德曰钦明恭让。舜之德曰温恭允塞。禹之德曰克勤克俭。不自满假。汤之德曰从谏弗咈。检身若不及。文王之德曰小心翼翼。子贡称夫子亦曰温良恭俭让。此乃千古圣贤相传印板。何尝有一毫自大自矜之心哉。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已。荆公文章节行。固可以高视流俗。惟其以此自足。便以为人莫己若。凌驾一世。不复虚心逊志。以求义理之无穷。而克伐之心胜焉。是其所长。反为所病而不可救药。又何以任天下之重。来天下之善。而成天下之务哉。春秋一经。亲出于圣人之手。游,夏以下不敢赞一辞。万世无敢议者。介甫断然以己意斥之为断烂朝报。经筵不以进读。科举废而不用。推此心以行于世。故上无所惮而以为天变不足畏。下无所忌而以为人言不足恤。天上地下。惟我独尊。猖狂妄行。无复顾藉。亦何所不至哉。神宗之所取于安石者在此。而明道之所忧于安石者。亦惟在于此。呜呼。非有正心克己之学者。其孰能辨之。他日其徒推尊介甫。配享学宫。犹为不满。至欲撤先圣之位而代之。人徒知此议出于蔡卞。而不知介甫平日之意固然也。杨龟山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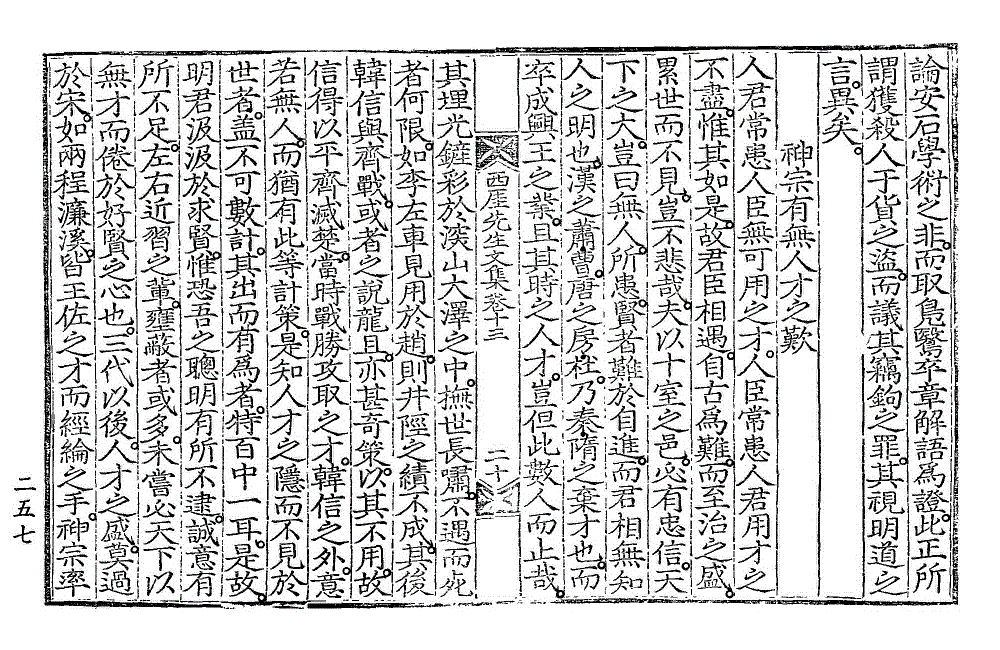 论安石学术之非。而取凫鹥卒章解语为證。此正所谓获杀人于货之盗。而议其窃钩之罪。其视明道之言。异矣。
论安石学术之非。而取凫鹥卒章解语为證。此正所谓获杀人于货之盗。而议其窃钩之罪。其视明道之言。异矣。神宗有无人才之叹
人君常患人臣无可用之才。人臣常患人君用才之不尽。惟其如是。故君臣相遇。自古为难。而至治之盛。累世而不见。岂不悲哉。夫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大。岂曰无人。所患。贤者难于自进。而君相无知人之明也。汉之萧,曹。唐之房,杜。乃秦,隋之弃才也。而卒成兴王之业。且其时之人才。岂但此数人而止哉。其埋光铲彩于深山大泽之中。抚世长啸。不遇而死者何限。如李左车见用于赵。则井陉之绩不成。其后韩信与齐战。或者之说龙且。亦甚奇策。以其不用。故信得以平齐灭楚。当时战胜攻取之才。韩信之外。意若无人。而犹有此等计策。是知人才之隐而不见于世者。盖不可数计。其出而有为者。特百中一耳。是故。明君汲汲于求贤。惟恐吾之聪明有所不逮。诚意有所不足。左右近习之辈。壅蔽者或多。未尝必天下以无才而倦于好贤之心也。三代以后。人才之盛。莫过于宋。如两程濂溪。皆王佐之才而经纶之手。神宗率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8H 页
 多置之于草泽閒散之中。朝夕所与论议咨问于细毡之上者。不过安石之馀党蒲宗孟,王圭,蔡确而止耳。及其春秋迟暮。朝廷日乱。事业之成。如捕风系影。然后乃始反顾惘然。临朝发叹。犹不知反求其所以然之故。而乃曰天下无人才。正韩子所谓其真无马耶。其真不知马也。岂天未欲平治天下。何其惑之甚耶。中庸九经。修身为上。尊贤次之。修身者。用贤之本也。而尊贤之目有四焉。去谗也。远色也。贱货也。贵德也。神宗有志于用贤。而未能去谗。所好者谗谄面谀之徒。宜其实德之不至也。
多置之于草泽閒散之中。朝夕所与论议咨问于细毡之上者。不过安石之馀党蒲宗孟,王圭,蔡确而止耳。及其春秋迟暮。朝廷日乱。事业之成。如捕风系影。然后乃始反顾惘然。临朝发叹。犹不知反求其所以然之故。而乃曰天下无人才。正韩子所谓其真无马耶。其真不知马也。岂天未欲平治天下。何其惑之甚耶。中庸九经。修身为上。尊贤次之。修身者。用贤之本也。而尊贤之目有四焉。去谗也。远色也。贱货也。贵德也。神宗有志于用贤。而未能去谗。所好者谗谄面谀之徒。宜其实德之不至也。蔡京等以绍述之说。误哲宗,徽宗。卒以亡宋。
人君秉天下之利。权天下之人。其贵贱贫富死生荣辱。皆决于人主之好恶。故君心之所好者。天下之所趋也。君心之所恶者。天下之所避也。小人巧于谋身。密于图利。日夜潜伺人主之意向而低䀚迎合。以中人主之心。人主本有是心。一闻小人之言。喜其与己同。欣然相合。如水流湿火就燥。人莫能间。而不知小人。故为此以中之也。战国之士如苏秦,张仪之流。欲图富贵而无其路。则习为揣摩阖辟之术。所至先观其君之意向。有惧则以惧而说之。有喜则以喜而入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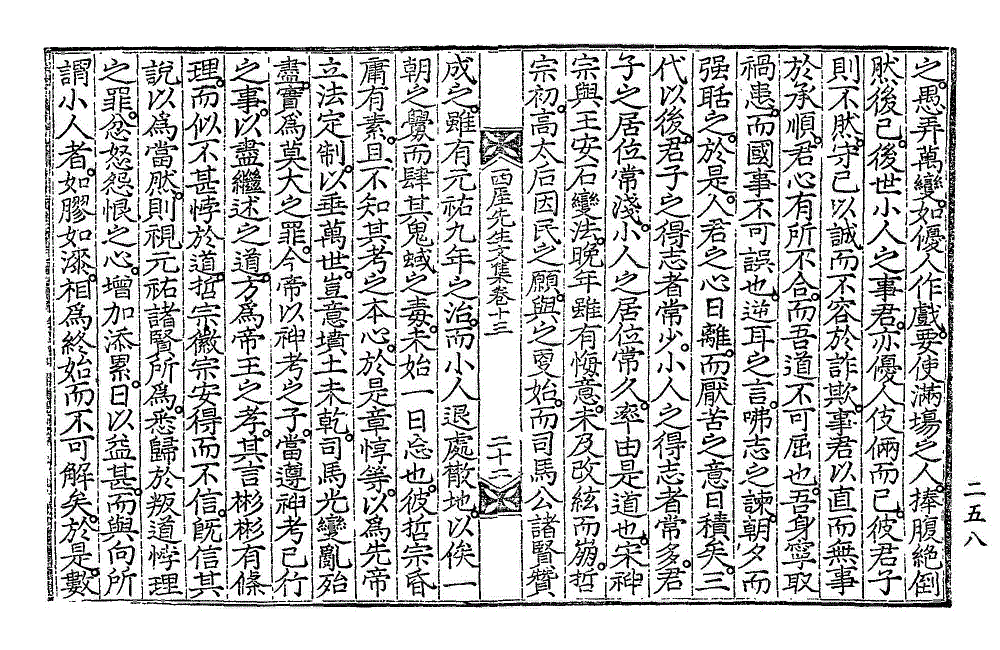 之。愚弄万变。如优人作戏。要使满场之人。捧腹绝倒然后已。后世小人之事君。亦优人伎俩而已。彼君子则不然。守己以诚而不容于诈欺。事君以直而无事于承顺。君心有所不合。而吾道不可屈也。吾身宁取祸患。而国事不可误也。逆耳之言。咈志之谏。朝夕而强聒之。于是。人君之心日离。而厌苦之意日积矣。三代以后。君子之得志者常少。小人之得志者常多。君子之居位常浅。小人之居位常久。率由是道也。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晚年虽有悔意。未及改弦而崩。哲宗初。高太后因民之愿。与之更始。而司马公诸贤赞成之。虽有元祐九年之治。而小人退处散地。以俟一朝之衅而肆其鬼蜮之毒。未始一日忘也。彼哲宗昏庸有素。且不知其考之本心。于是章惇等。以为先帝立法定制。以垂万世。岂意坟土未乾。司马光变乱殆尽。实为莫大之罪。今帝以神考之子。当遵神考已行之事。以尽继述之道。方为帝王之孝。其言彬彬有条理。而似不甚悖于道。哲宗,徽宗安得而不信。既信其说以为当然。则视元祐诸贤所为。悉归于叛道悖理之罪。忿怒怨恨之心。增加添累。日以益甚。而与向所谓小人者。如胶如漆。相为终始而不可解矣。于是。数
之。愚弄万变。如优人作戏。要使满场之人。捧腹绝倒然后已。后世小人之事君。亦优人伎俩而已。彼君子则不然。守己以诚而不容于诈欺。事君以直而无事于承顺。君心有所不合。而吾道不可屈也。吾身宁取祸患。而国事不可误也。逆耳之言。咈志之谏。朝夕而强聒之。于是。人君之心日离。而厌苦之意日积矣。三代以后。君子之得志者常少。小人之得志者常多。君子之居位常浅。小人之居位常久。率由是道也。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晚年虽有悔意。未及改弦而崩。哲宗初。高太后因民之愿。与之更始。而司马公诸贤赞成之。虽有元祐九年之治。而小人退处散地。以俟一朝之衅而肆其鬼蜮之毒。未始一日忘也。彼哲宗昏庸有素。且不知其考之本心。于是章惇等。以为先帝立法定制。以垂万世。岂意坟土未乾。司马光变乱殆尽。实为莫大之罪。今帝以神考之子。当遵神考已行之事。以尽继述之道。方为帝王之孝。其言彬彬有条理。而似不甚悖于道。哲宗,徽宗安得而不信。既信其说以为当然。则视元祐诸贤所为。悉归于叛道悖理之罪。忿怒怨恨之心。增加添累。日以益甚。而与向所谓小人者。如胶如漆。相为终始而不可解矣。于是。数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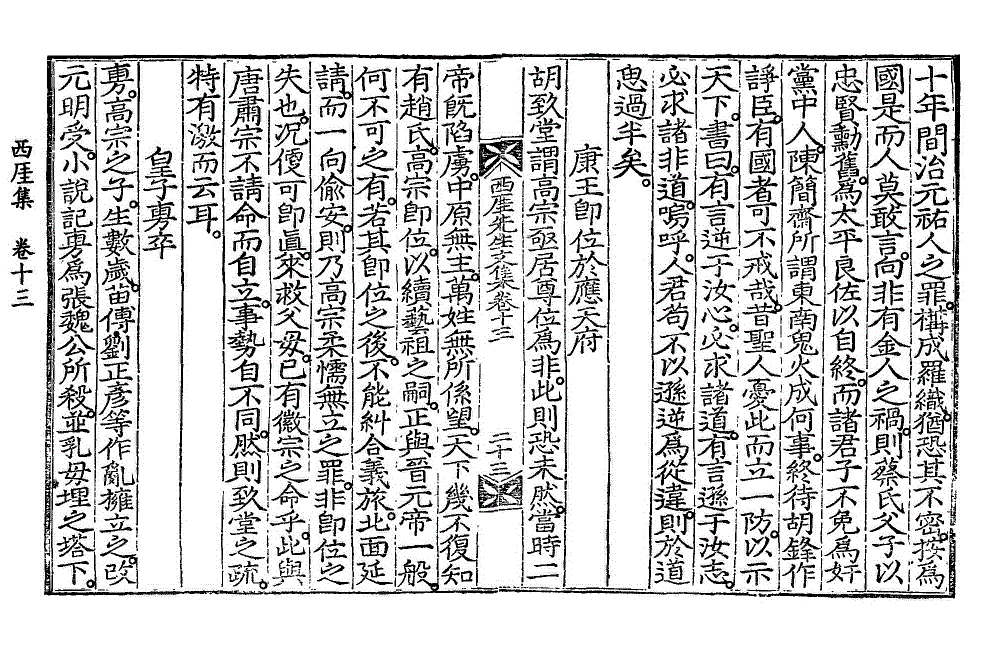 十年间治元祐人之罪。构成罗织。犹恐其不密。按为国是而人莫敢言。向非有金人之祸。则蔡氏父子以忠贤勋旧。为太平良佐以自终。而诸君子不免为奸党中人。陈简斋所谓东南鬼火成何事。终待胡锋作诤臣。有国者可不戒哉。昔圣人忧此而立一防。以示天下。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呜呼。人君苟不以逊逆为从违。则于道思过半矣。
十年间治元祐人之罪。构成罗织。犹恐其不密。按为国是而人莫敢言。向非有金人之祸。则蔡氏父子以忠贤勋旧。为太平良佐以自终。而诸君子不免为奸党中人。陈简斋所谓东南鬼火成何事。终待胡锋作诤臣。有国者可不戒哉。昔圣人忧此而立一防。以示天下。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呜呼。人君苟不以逊逆为从违。则于道思过半矣。康王即位于应天府
胡致堂谓高宗亟居尊位为非。此则恐未然。当时二帝既陷虏。中原无主。万姓无所系望。天下几不复知有赵氏。高宗即位。以续艺祖之嗣。正与晋元帝一般。何不可之有。若其即位之后。不能纠合义旅。北面延请。而一向偷安。则乃高宗柔懦无立之罪。非即位之失也。况便可即真。来救父母。已有徽宗之命乎。此与唐肃宗不请命而自立。事势自不同。然则致堂之疏。特有激而云耳。
皇子敷卒
敷。高宗之子。生数岁。苗傅,刘正彦等作乱拥立之。改元明受。小说记敷为张魏公所杀。并乳母埋之塔下。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59L 页
 盖以己奸大位故也。其后高宗卒无他子。晚年以此恶魏公。有宁亡国。不用张浚之语云。然此大事。而宋史不书。何欤。岂作史者为魏公讳耶。敷在襁褓中。奸位非其所知。唐昭宗犹不听朱全忠杀德王裕。魏公处置。殊未可晓。不然则小说所载。不可信也。大抵魏公负气。勇于作事。而其病多在疏脱。朱胜非谓喜事而疏。实魏公四字好题目。
盖以己奸大位故也。其后高宗卒无他子。晚年以此恶魏公。有宁亡国。不用张浚之语云。然此大事。而宋史不书。何欤。岂作史者为魏公讳耶。敷在襁褓中。奸位非其所知。唐昭宗犹不听朱全忠杀德王裕。魏公处置。殊未可晓。不然则小说所载。不可信也。大抵魏公负气。勇于作事。而其病多在疏脱。朱胜非谓喜事而疏。实魏公四字好题目。李纲,张浚
南渡后人才。当以李伯纪为第一。武将则岳武穆。二人者。可当恢复之责。其馀则未见有卓然可倚者。或曰。张德远如何。曰。志大而才疏。忠有馀而识不足。明儒谓宋之亡。德远为之。其论虽过。要亦有近似者。高宗初立。因人望起李伯纪为相。此中兴一大机轴。所患者。伯纪但一人。而汪,黄诸小人左右掣肘者多也。德远不劝高宗任贤勿贰。去邪勿疑。以责成效。顾乃党附潜善。偏私宋齐愈。首先攻之。何意也。且李公忠谋伟略。已见于围城之日。天下军民举知之矣。而德远独不知乎。李公既去。汪,黄专国。置国事于度外。日听浮屠说法于政事堂。德远于是乃上书。请讲御敌之策。此犹强僬侥以千匀之重。曾不满识者之一哂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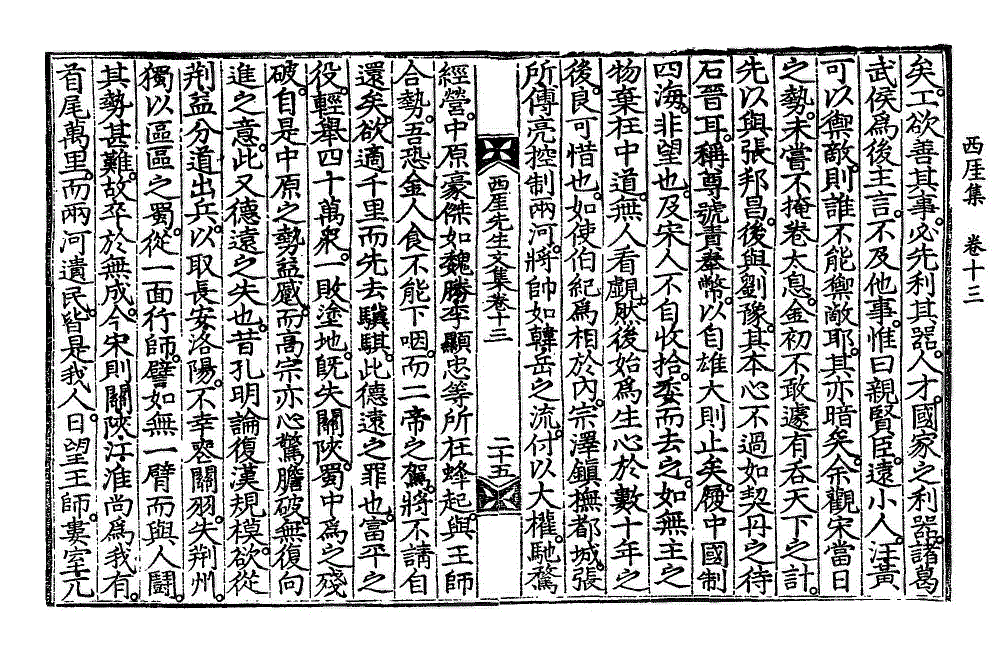 矣。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才。国家之利器。诸葛武侯为后主言。不及他事。惟曰亲贤臣。远小人。汪,黄可以御敌。则谁不能御敌耶。其亦暗矣。余观宋当日之势。未尝不掩卷太息。金初不敢遽有吞天下之计。先以与张邦昌。后与刘豫。其本心不过如契丹之待石晋耳。称尊号责奉币。以自雄大则止矣。履中国制四海。非望也。及宋人不自收拾。委而去之。如无主之物弃在中道。无人看觑。然后始为生心于数十年之后。良可惜也。如使伯纪为相于内。宗泽镇抚都城。张所傅亮控制两河。将帅如韩,岳之流。付以大权。驰骛经营。中原豪杰如魏胜李显忠等所在蜂起。与王师合势。吾恐金人食不能下咽。而二帝之驾。将不请自还矣。欲适千里而先去骥骐。此德远之罪也。富平之役。轻举四十万众。一败涂地。既失关陕。蜀中为之残破。自是中原之势益蹙。而高宗亦心惊胆破。无复向进之意。此又德远之失也。昔孔明论复汉规模。欲从荆,益分道出兵。以取长安,洛阳。不幸丧关羽。失荆州。独以区区之蜀。从一面行师。譬如无一臂而与人斗。其势甚难。故卒于无成。今宋则关,陕,江,淮尚为我有。首尾万里。而两河遗民。皆是我人。日望王师。娄室,兀
矣。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才。国家之利器。诸葛武侯为后主言。不及他事。惟曰亲贤臣。远小人。汪,黄可以御敌。则谁不能御敌耶。其亦暗矣。余观宋当日之势。未尝不掩卷太息。金初不敢遽有吞天下之计。先以与张邦昌。后与刘豫。其本心不过如契丹之待石晋耳。称尊号责奉币。以自雄大则止矣。履中国制四海。非望也。及宋人不自收拾。委而去之。如无主之物弃在中道。无人看觑。然后始为生心于数十年之后。良可惜也。如使伯纪为相于内。宗泽镇抚都城。张所傅亮控制两河。将帅如韩,岳之流。付以大权。驰骛经营。中原豪杰如魏胜李显忠等所在蜂起。与王师合势。吾恐金人食不能下咽。而二帝之驾。将不请自还矣。欲适千里而先去骥骐。此德远之罪也。富平之役。轻举四十万众。一败涂地。既失关陕。蜀中为之残破。自是中原之势益蹙。而高宗亦心惊胆破。无复向进之意。此又德远之失也。昔孔明论复汉规模。欲从荆,益分道出兵。以取长安,洛阳。不幸丧关羽。失荆州。独以区区之蜀。从一面行师。譬如无一臂而与人斗。其势甚难。故卒于无成。今宋则关,陕,江,淮尚为我有。首尾万里。而两河遗民。皆是我人。日望王师。娄室,兀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0L 页
 朮又岂与司马懿等乎。如此而不能有为。人才高下。可以想见。宋人或以德远比忠武侯。儗人必于伦。岂谓是耶。且孔明能容法孝直。不以好尚同异而弃其所长。德远不能容李伯纪,赵元镇。又以一言不合。夺岳武穆军。遂致郦琼之变。古云心不错者。可以处大事。智不外者。可以统大众。德远皆无之。无惑乎功业之不成也。
朮又岂与司马懿等乎。如此而不能有为。人才高下。可以想见。宋人或以德远比忠武侯。儗人必于伦。岂谓是耶。且孔明能容法孝直。不以好尚同异而弃其所长。德远不能容李伯纪,赵元镇。又以一言不合。夺岳武穆军。遂致郦琼之变。古云心不错者。可以处大事。智不外者。可以统大众。德远皆无之。无惑乎功业之不成也。汪,黄为左右相入贺。帝曰何患国事不济。
人君居天下标准之地。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使天下之曲直邪正。皆得以取正于斯。夫是之谓建极。今高宗之好恶取舍。倒置如此。岂不怪哉。千载之下。可发一笑。传曰。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高宗有焉。
杀陈东欧阳澈
宋立国。以忠厚为本。待士大夫以礼。二百年间。未有以言得重罪者。高宗之为君。过于柔弱则有之。非残忍刻暴之资。今乃发怒于二人。至戮诸东市。如治逆乱。略不爱惜。独何欤。曰。此亦高宗过于柔弱者为之祟也。奸臣之巧弄其君。其术万端。必乘其心之暗处而得售其奸。高宗性本恇㥘。过于畏忌。陈东曾与都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1H 页
 人数万。伏阙救李纲。至杀近侍。宣纲后期者。高宗见有此事。一朝见东姓名。恐其复然。而潜善知其意。遂以危论激之。以成其祸。呜呼。当国家新造未集之初。既流窜柱石之佐。又杀忠义直言之士。与唐僖宗杀孟昭图无异。然则宋之得保一隅。不即灭亡。亦幸耳。噫。
人数万。伏阙救李纲。至杀近侍。宣纲后期者。高宗见有此事。一朝见东姓名。恐其复然。而潜善知其意。遂以危论激之。以成其祸。呜呼。当国家新造未集之初。既流窜柱石之佐。又杀忠义直言之士。与唐僖宗杀孟昭图无异。然则宋之得保一隅。不即灭亡。亦幸耳。噫。罢河东经制司召傅亮还
傅亮为人。不知如何。然李纲举之。必有所取也。时金人虽蹂躏中原。而两河尚未尽汲。豪杰各自团保。以待王人者。不可胜数。李公建遣二人收两河。乃至急必行之计。彼潜善,伯彦沮挠百端者。非以其策为不可也。特借其事以沮李公。而使不安于在朝也。得失分明。昭若黑白。而高宗犹不能主张。终使奸计得行。李公至以去就争之而不得。其不可与有为也决矣。是故。天运于上而后四时五行宣其气。未有人君不能自强。而臣下独能有为者。如燕昭,汉光武皆身定大计。毅然不动。精神折冲。故乐毅,寇,邓之属。不过承其指挥而各效才智耳。不然。惟相率而去尔。亦何济事之有哉。或问晋元帝,宋高宗孰优。曰。其施为气象。大略鲁,卫之间耳。然元帝犹信任王导。虽刘隗,刁协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1L 页
 等日夕谤毁。而竟以周顗之言。寄百里之命。使高宗当此。恐不能然也。以此言之。元帝差强乎尔。
等日夕谤毁。而竟以周顗之言。寄百里之命。使高宗当此。恐不能然也。以此言之。元帝差强乎尔。安置张所于岭南
张所为河北招抚。未及赴司而罢。有何可窜之罪。特以为李伯纪所用而迁怒至此。其亦甚矣。盗憎主人。主人非有所得罪于盗。小人之于君子。亦若是而已。
议幸南阳
李纲言车驾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纵未能行上策。且适襄,邓。示不忘故都。以系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复我有。至哉。言乎。天下之势。不进则退。六军万姓之心胆。都在一人之身。观其进退。而人心一齐前却。柰高宗之心本无中原之意。惟僻居偷安是事。他日张浚屡请幸建康。此仅李公所谓下策。而犹不从。况进乎此者乎。使伯纪在朝。高宗临安之志不遂。虽外不能公拒正议。面与唯诺。而内实忌惮。若芒刺在背。汪,黄左腹投间之说。其甘如蜜。诗云。盗言孔甘。乱是用长。其是之谓乎。后秦桧中高宗亦如是。盖和是高宗本心。以此能固结其宠。终身在相位而不去也。
李伯纪甲寅封事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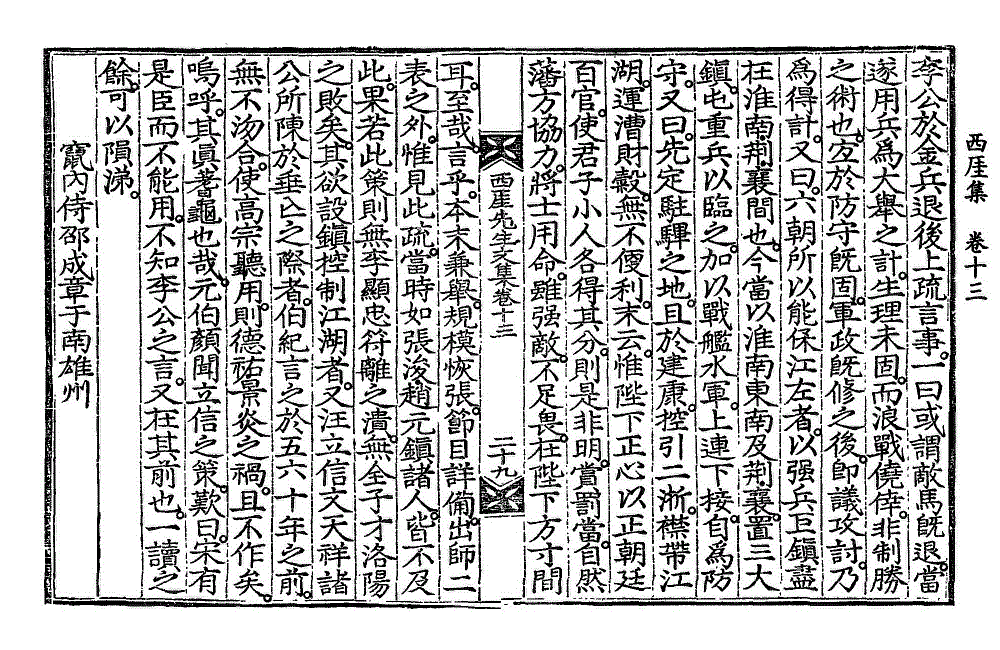 李公于金兵退后上疏言事。一曰或谓敌马既退。当遂用兵为大举之计。生理未固。而浪战侥倖。非制胜之术也。宜于防守既固。军政既修之后。即议攻讨。乃为得计。又曰。六朝所以能保江左者。以强兵巨镇尽在淮南,荆,襄间也。今当以淮南东南及荆,襄。置三大镇。屯重兵以临之。加以战舰水军。上连下接。自为防守。又曰。先定驻跸之地。且于建康。控引二浙。襟带江湖。运漕财谷。无不便利。末云。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则是非明。赏罚当。自然藩方协力。将士用命。虽强敌。不足畏。在陛下方寸间耳。至哉。言乎。本末兼举。规模恢张。节目详备。出师二表之外。惟见此疏。当时如张浚,赵元镇诸人。皆不及此。果若此策则无李显忠符离之溃。无全子才洛阳之败矣。其欲设镇控制江湖者。又汪立信文天祥诸公所陈于垂亡之际者。伯纪言之于五六十年之前。无不沕合。使高宗听用。则德祐,景炎之祸。且不作矣。呜呼。其真蓍龟也哉。元伯颜闻立信之策。叹曰。宋有是臣而不能用。不知李公之言。又在其前也。一读之馀。可以陨涕。
李公于金兵退后上疏言事。一曰或谓敌马既退。当遂用兵为大举之计。生理未固。而浪战侥倖。非制胜之术也。宜于防守既固。军政既修之后。即议攻讨。乃为得计。又曰。六朝所以能保江左者。以强兵巨镇尽在淮南,荆,襄间也。今当以淮南东南及荆,襄。置三大镇。屯重兵以临之。加以战舰水军。上连下接。自为防守。又曰。先定驻跸之地。且于建康。控引二浙。襟带江湖。运漕财谷。无不便利。末云。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则是非明。赏罚当。自然藩方协力。将士用命。虽强敌。不足畏。在陛下方寸间耳。至哉。言乎。本末兼举。规模恢张。节目详备。出师二表之外。惟见此疏。当时如张浚,赵元镇诸人。皆不及此。果若此策则无李显忠符离之溃。无全子才洛阳之败矣。其欲设镇控制江湖者。又汪立信文天祥诸公所陈于垂亡之际者。伯纪言之于五六十年之前。无不沕合。使高宗听用。则德祐,景炎之祸。且不作矣。呜呼。其真蓍龟也哉。元伯颜闻立信之策。叹曰。宋有是臣而不能用。不知李公之言。又在其前也。一读之馀。可以陨涕。窜内侍邵成章于南雄州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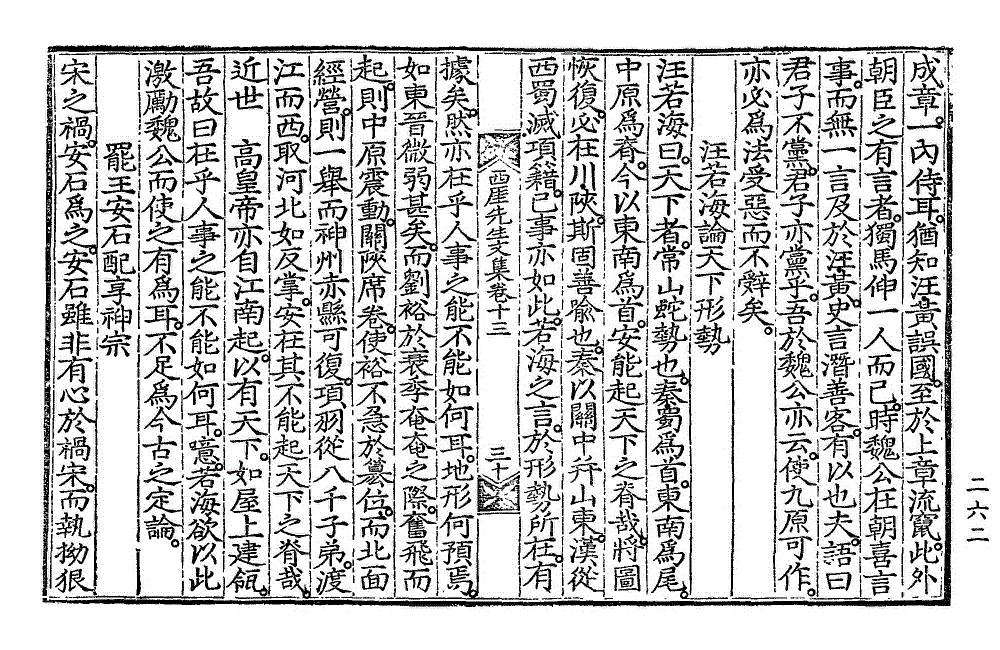 成章。一内侍耳。犹知汪,黄误国。至于上章流窜。此外朝臣之有言者。独马伸一人而已。时魏公在朝喜言事。而无一言及于汪,黄。史言潜善客。有以也夫。语曰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吾于魏公亦云。使九原可作。亦必为法受恶而不辞矣。
成章。一内侍耳。犹知汪,黄误国。至于上章流窜。此外朝臣之有言者。独马伸一人而已。时魏公在朝喜言事。而无一言及于汪,黄。史言潜善客。有以也夫。语曰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吾于魏公亦云。使九原可作。亦必为法受恶而不辞矣。汪若海论天下形势
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陜。斯固善喻也。秦以关中并山东。汉从西蜀灭项籍。已事亦如此。若海之言。于形势所在。有据矣。然亦在乎人事之能不能如何耳。地形何预焉。如东晋微弱甚矣。而刘裕于衰季奄奄之际。奋飞而起。则中原震动。关陜席卷。使裕不急于篡位。而北面经营。则一举而神州赤县可复。项羽从八千子弟。渡江而西。取河北如反掌。安在其不能起天下之脊哉。近世 高皇帝亦自江南起。以有天下。如屋上建瓴。吾故曰在乎人事之能不能如何耳。噫。若海欲以此激励魏公而使之有为耳。不足为今古之定论。
罢王安石配享神宗
宋之祸。安石为之。安石虽非有心于祸宋。而执拗狠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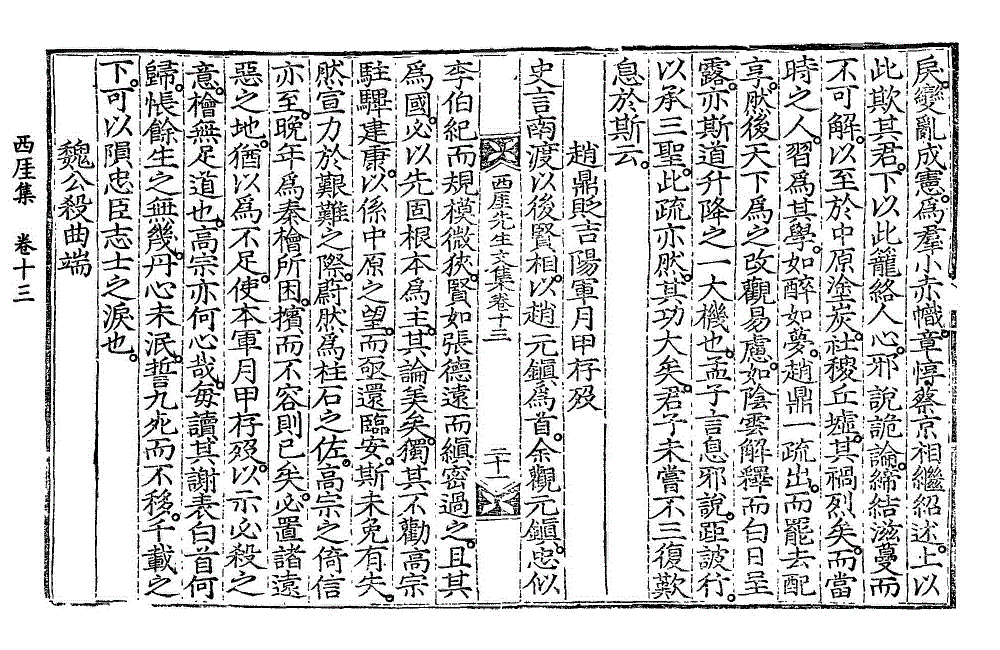 戾。变乱成宪。为群小赤帜。章惇,蔡京相继绍述。上以此欺其君。下以此笼络人心。邪说诡论。缔结滋蔓而不可解。以至于中原涂炭。社稷丘墟。其祸烈矣。而当时之人。习为其学。如醉如梦。赵鼎一疏出。而罢去配享。然后天下为之改观易虑。如阴云解释而白日呈露。亦斯道升降之一大机也。孟子言息邪说。距诐行。以承三圣。此疏亦然。其功大矣。君子未尝不三复叹息于斯云。
戾。变乱成宪。为群小赤帜。章惇,蔡京相继绍述。上以此欺其君。下以此笼络人心。邪说诡论。缔结滋蔓而不可解。以至于中原涂炭。社稷丘墟。其祸烈矣。而当时之人。习为其学。如醉如梦。赵鼎一疏出。而罢去配享。然后天下为之改观易虑。如阴云解释而白日呈露。亦斯道升降之一大机也。孟子言息邪说。距诐行。以承三圣。此疏亦然。其功大矣。君子未尝不三复叹息于斯云。赵鼎贬吉阳军月甲存殁
史言南渡以后贤相。以赵元镇为首。余观元镇。忠似李伯纪而规模微狭。贤如张德远而缜密过之。且其为国。必以先固根本为主。其论美矣。独其不劝高宗驻跸建康。以系中原之望。而亟还临安。斯未免有失。然宣力于艰难之际。蔚然为柱石之佐。高宗之倚信亦至。晚年为秦桧所困。摈而不容则已矣。必置诸远恶之地。犹以为不足。使本军月甲存殁。以示必杀之意。桧无足道也。高宗亦何心哉。每读其谢表白首何归。怅馀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而不移。千载之下。可以陨忠臣志士之泪也。
魏公杀曲端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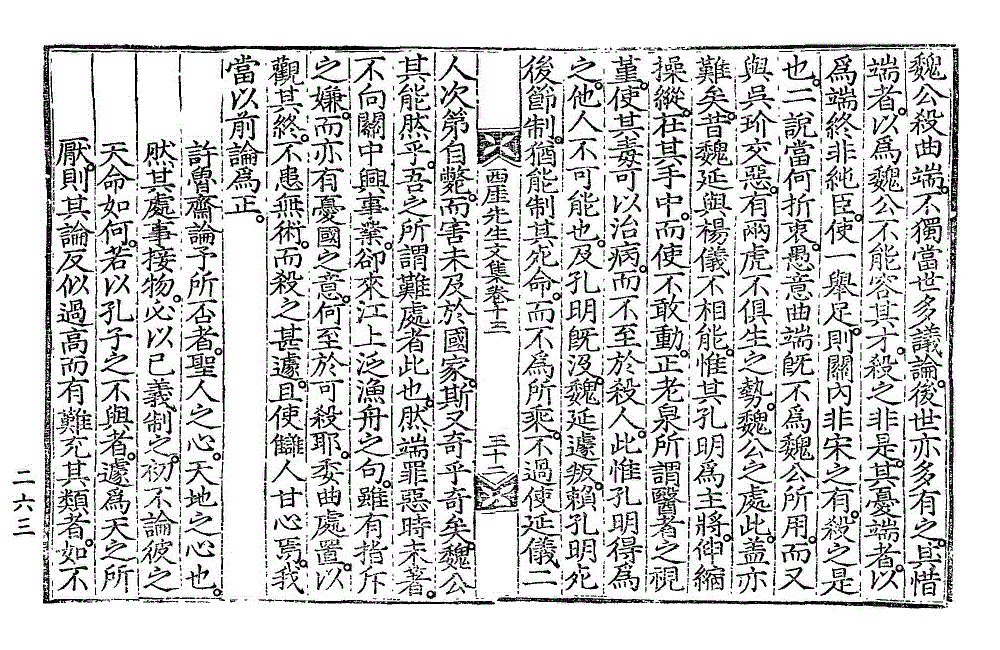 魏公杀曲端。不独当世多议论。后世亦多有之。其惜端者。以为魏公不能容其才。杀之非是。其忧端者。以为端终非纯臣。使一举足。则关内非宋之有。杀之是也。二说当何折衷。愚意曲端既不为魏公所用。而又与吴玠交恶。有两虎不俱生之势。魏公之处此。盖亦难矣。昔魏延与杨仪不相能。惟其孔明为主将。伸缩操纵。在其手中。而使不敢动。正老泉所谓医者之视堇。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于杀人。此惟孔明得为之。他人不可能也。及孔明既没。魏延遽叛。赖孔明死后节制。犹能制其死命。而不为所乘。不过使延仪二人次第自毙。而害未及于国家。斯又奇乎奇矣。魏公其能然乎。吾之所谓难处者此也。然端罪恶时未著。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之句。虽有指斥之嫌。而亦有忧国之意。何至于可杀耶。委曲处置。以观其终。不患无术。而杀之甚遽。且使雠人甘心焉。我当以前论为正。
魏公杀曲端。不独当世多议论。后世亦多有之。其惜端者。以为魏公不能容其才。杀之非是。其忧端者。以为端终非纯臣。使一举足。则关内非宋之有。杀之是也。二说当何折衷。愚意曲端既不为魏公所用。而又与吴玠交恶。有两虎不俱生之势。魏公之处此。盖亦难矣。昔魏延与杨仪不相能。惟其孔明为主将。伸缩操纵。在其手中。而使不敢动。正老泉所谓医者之视堇。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于杀人。此惟孔明得为之。他人不可能也。及孔明既没。魏延遽叛。赖孔明死后节制。犹能制其死命。而不为所乘。不过使延仪二人次第自毙。而害未及于国家。斯又奇乎奇矣。魏公其能然乎。吾之所谓难处者此也。然端罪恶时未著。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之句。虽有指斥之嫌。而亦有忧国之意。何至于可杀耶。委曲处置。以观其终。不患无术。而杀之甚遽。且使雠人甘心焉。我当以前论为正。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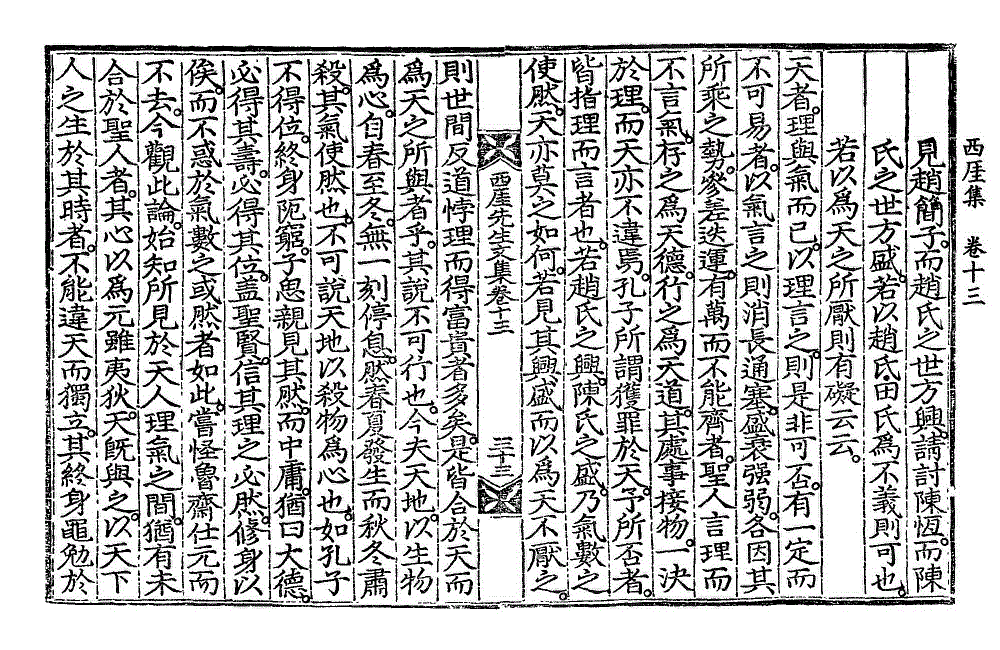 许鲁斋论予所否者。圣人之心。天地之心也。然其处事接物。必以己义制之。初不论彼之天命如何。若以孔子之不与者。遽为天之所厌。则其论反似过高而有难充其类者。如不见赵简子。而赵氏之世方兴。请讨陈恒。而陈氏之世方盛。若以赵氏,田氏为不义则可也。若以为天之所厌则有碍云云。
许鲁斋论予所否者。圣人之心。天地之心也。然其处事接物。必以己义制之。初不论彼之天命如何。若以孔子之不与者。遽为天之所厌。则其论反似过高而有难充其类者。如不见赵简子。而赵氏之世方兴。请讨陈恒。而陈氏之世方盛。若以赵氏,田氏为不义则可也。若以为天之所厌则有碍云云。天者。理与气而已。以理言之。则是非可否。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以气言之则消长通塞。盛衰强弱。各因其所乘之势。参差迭运。有万而不能齐者。圣人言理而不言气。存之为天德。行之为天道。其处事接物。一决于理。而天亦不违焉。孔子所谓获罪于天。予所否者。皆指理而言者也。若赵氏之兴。陈氏之盛。乃气数之使然。天亦莫之如何。若见其兴盛而以为天不厌之。则世间反道悖理而得富贵者多矣。是皆合于天而为天之所与者乎。其说不可行也。今夫天地。以生物为心。自春至冬。无一刻停息。然春夏发生而秋冬肃杀。其气使然也。不可说天地以杀物为心也。如孔子不得位。终身阨穷。子思亲见其然。而中庸。犹曰大德。必得其寿。必得其位。盖圣贤。信其理之必然。修身以俟。而不惑于气数之或然者如此。尝怪鲁斋仕元而不去。今观此论。始知所见于天人理气之间。犹有未合于圣人者。其心以为元虽夷狄。天既与之。以天下人之生于其时者。不能违天而独立。其终身黾勉于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4L 页
 被发左衽之间。而不以为辱者。意其在此也。然则伯夷饿死首阳。未必为仁。而冉有从季氏。亦不必见绝于圣门矣。呜呼。鲁斋有圣贤之学。陋儒议论。所不敢到。姑书此。将以取正于尚论知道之君子云。
被发左衽之间。而不以为辱者。意其在此也。然则伯夷饿死首阳。未必为仁。而冉有从季氏。亦不必见绝于圣门矣。呜呼。鲁斋有圣贤之学。陋儒议论。所不敢到。姑书此。将以取正于尚论知道之君子云。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杂著○丧葬质疑
治棺
按杉。未详何木。我国为棺椁。上下通用松板。不见用杉。或云朱子讳韦斋名作杉。其实杉亦松。然东坡诗旋斫杉松。字会亦云杉。松类。其非一物明矣。岂杉不产于我国。虽产而人无知者。故遂废而不用耶。为可惜也。油杉土杉。似是一物而以性品分上下耳。今松板中。坚而粗理色黄赤。入土年久不腐者为上。小理而色白。柔软不坚者为下品。杉之分上下。亦应如此耳。柏。今人指海松结实如巴豆者为柏。非也。今之所谓侧柏是也。而人未尝取以为棺椁。故其材之中用与否。未可知。亦绝难得大者也。丧葬之具。莫重于棺椁。而取材不广。名且不能辨。况于用乎。姑记之。将问于博物者。
更按礼记。天子柏棺。诸侯松棺。大夫柏棺。盖柏胜于松。故天子用柏。诸侯嫌于逼。故用松而不敢用柏。大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5H 页
 夫位下而无嫌。故得用柏。疏家之说如此。又程子论棺椁。有松千柏万之说。而并不言杉为可用何也。甚可疑。
夫位下而无嫌。故得用柏。疏家之说如此。又程子论棺椁。有松千柏万之说。而并不言杉为可用何也。甚可疑。秫灰
按本草。秫。似黍米而粒小。即诗之所谓稌也。性宜下湿而暑。故东南多有之。宜作酒。陶渊明在彭泽种秫者。亦此物也。贡生权英俊言尝在俞政丞泓家。见一字书。云秫黑黍也。以此知秫乃黍类。古人于棺内。不用他物而用秫灰。必有其意。我国人不识秫为何物。或误以为粘稻。治棺之时。多烧粘稻作灰。其有力者作米烧灰用之。皆无意义。吾家亦未免从俗为之。至今以为恨。然余少时。在弘文馆见杂书。记我国物产而云无秫。果然则虽欲用之而不可得。当更问于老农之知谷性者以定耳。
灰漆
其法未详。今之治棺者。但于入棺后。漆布涂棺外合木之缝而已。其内不用漆。且漆必经日乃凝。仓卒虽欲用之。恐势有所不可。惟平时预作寿器者。乃可用。然礼文既云内外皆用灰漆。则必有其法。而特今人未讲耳。且不知所谓灰者何物。今漆工用骨灰和漆。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5L 页
 涂器物。甚滑泽。然棺中不宜用骨灰。疑是石灰。或蜃灰耳。当试用以验其良否耳。更详之。
涂器物。甚滑泽。然棺中不宜用骨灰。疑是石灰。或蜃灰耳。当试用以验其良否耳。更详之。沥青
古人治棺。最重沥青。葬时用薄板。亦要用沥青故耳。然其造法。今不可晓。我国亦有所谓沥青者。用以漆器。只取生色而已。以此知我国沥青。非中国之沥青也。高氏云。以少蚌粉,黄蜡,清油合煎之。乃可用。不然则裂矣。以此观之。其造法可意会。必以松脂为主。而略加三物。合煎以成也。至朱子之丧。蔡氏兄弟主用松脂。不用油蜡。以为松脂不得全其性。然但云去油蜡。而不言去蚌粉。则以蚌粉合煎松脂无疑也。蔡氏于此。必有明见。盖蚌粉。即古之所谓蜃灰。宋文公之丧。华元始用蜃灰。此则必以蜃灰代石灰。填实于圹内。宋又非滨海之国。取之必难。故君子讥其过制。若杂于松脂而用之。则所入至少。且不费力。何害于义也。近试以松脂十分。加蚌粉三分。黄蜡清油少许。合煎溶化。既凝之后。以物叩之。琤琤有金石声。性甚坚完。且无燥裂之患。与单用松脂不同。似为有益。第未知入土岁久后坚否又如何耳。刘氏以为斧斤不能加。得于亲见云。此必非浪说。而彭止堂又以为宜于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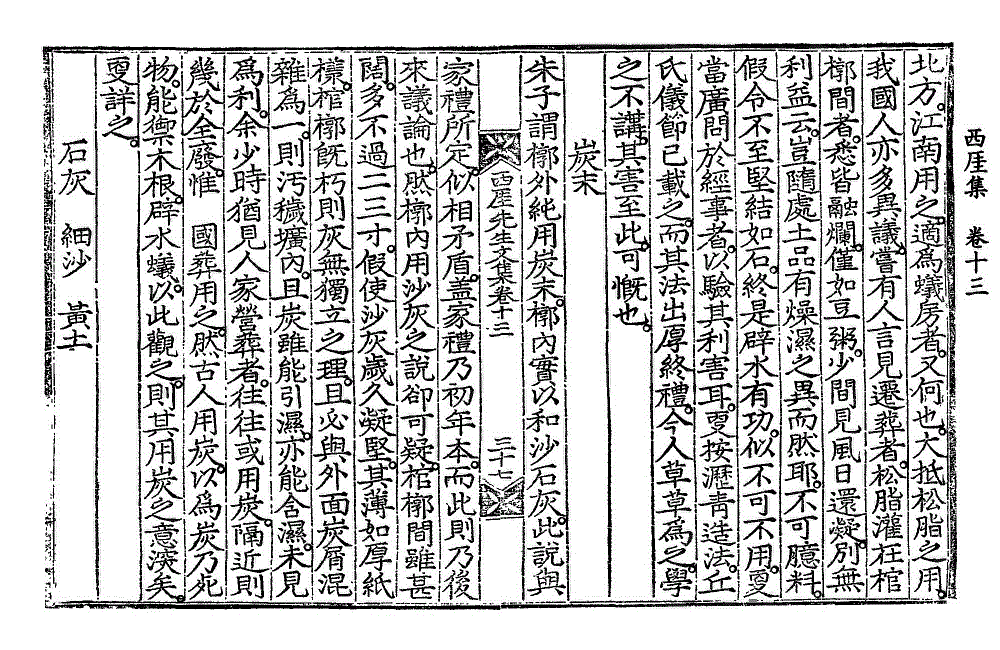 北方。江南用之。适为蚁房者。又何也。大抵松脂之用。我国人亦多异议。尝有人言见迁葬者。松脂灌在棺椁间者。悉皆融烂。仅如豆粥。少间见风日还凝。别无利益云。岂随处土品有燥湿之异而然耶。不可臆料。假令不至坚结如石。终是辟水有功。似不可不用。更当广问于经事者。以验其利害耳。更按沥青造法。丘氏仪节已载之。而其法出厚终礼。今人草草为之。学之不讲。其害至此。可慨也。
北方。江南用之。适为蚁房者。又何也。大抵松脂之用。我国人亦多异议。尝有人言见迁葬者。松脂灌在棺椁间者。悉皆融烂。仅如豆粥。少间见风日还凝。别无利益云。岂随处土品有燥湿之异而然耶。不可臆料。假令不至坚结如石。终是辟水有功。似不可不用。更当广问于经事者。以验其利害耳。更按沥青造法。丘氏仪节已载之。而其法出厚终礼。今人草草为之。学之不讲。其害至此。可慨也。炭末
朱子谓椁外纯用炭末。椁内实以和沙石灰。此说与家礼所定。似相矛盾。盖家礼乃初年本。而此则乃后来议论也。然椁内用沙灰之说却可疑。棺椁间虽甚阔。多不过二三寸。假使沙灰岁久凝坚。其薄如厚纸样。棺椁既朽则灰无独立之理。且必与外面炭屑混杂为一。则污秽圹内。且炭虽能引湿。亦能含湿。未见为利。余少时犹见人家营葬者。往往或用炭。隔近则几于全废。惟 国葬用之。然古人用炭。以为炭乃死物。能御木根。辟水蚁。以此观之。则其用炭之意深矣。更详之。
石灰 细沙 黄土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6L 页
 灰三分。沙土各一分。使灰得土而粘。得沙而坚。此家礼所定也。朱子后论此则以为当但用细沙和灰。黄土引木根。不可用之云。此说亦有异同。当何所定。然灰沙皆是燥物无液。终难粘结。恐当以家礼为定。若疑其引木则黄土比细沙略减分数用之无妨。且每观人家葬时。三物各置一处。临时斗量。不能均一相和。故细沙与黄土或多或少。不相乳入。今拟将三物筛去杂物后。又斗量相杂重筛。如医人剂药筛末之法。则灰与沙土。多少均适。无偏多偏少之处矣。
灰三分。沙土各一分。使灰得土而粘。得沙而坚。此家礼所定也。朱子后论此则以为当但用细沙和灰。黄土引木根。不可用之云。此说亦有异同。当何所定。然灰沙皆是燥物无液。终难粘结。恐当以家礼为定。若疑其引木则黄土比细沙略减分数用之无妨。且每观人家葬时。三物各置一处。临时斗量。不能均一相和。故细沙与黄土或多或少。不相乳入。今拟将三物筛去杂物后。又斗量相杂重筛。如医人剂药筛末之法。则灰与沙土。多少均适。无偏多偏少之处矣。淡酒
此用以洒灰。使坚实者也。然用酒之意未详。近人有迁葬旧墓者。多言开圹之后尚有酒臭在于灰间。而皆不凝硬。以手掬取。虚软无力。其无酒气处。却稍坚凝。以此知用酒洒灰。有害而无利。惟用榆皮汁和灰坚筑者实。皆凝结如石云。此则得于目见之说。非浪传无据。淡酒虽在礼文。今惧不敢用。只从俗用榆汁代之。
铁钉 铁镮
此古人治棺之具。钉盖用以合板。而镮则以索贯以举棺者也。今则天地盖。皆以木为银钉。不用铁物。其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7H 页
 制极好。虽违礼文。从俗可也。
制极好。虽违礼文。从俗可也。作灰隔
家礼不用椁。故隔板有二。其在内者。所以隔沥青与三物也。在外者。所以隔三物与炭屑也。在内者仍存。在外者抽出。所以不同也。既下棺。又用二板。一则在棺上。以隔沥青。使不透棺。一则在沥青之外。使沥青不杂于三物。所谓加灰隔内外盖者然也。今人用椁。又不用炭屑。则薄板诚无所施。今于下外棺之前。先用薄板如椁之状。四面实以三物而坚筑之。既毕。抽去其板。始下外棺当中。四隅有空分或一寸二寸。其间以蚌粉松脂灌之。凝结如椁。然后又下棺于椁内。加外盖。又以蚌粉松脂灌于四面及上。相合为一。无有罅缝。始以薄板一叶加其上。以隔松脂。然后实以三物而渐筑之。庶几不戾于古人之法。而有益于永久之图矣。(加薄板事。更议以定。)
实灰
按家礼。既下三物。恐震柩中。故不敢筑。但多用之。以俟其实。实土每尺许。即轻手筑之。勿令震动柩中。实土及半。藏明器下志石。然后复实以土而坚筑之。犹不敢肆意筑之。但令密杵坚筑云。礼文之意。于此极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267L 页
 加详审。不敢以但欲坚固之故。使之震动柩中。余屡见人家葬事。自下灰未及尺许。而役夫踊跃筑杵。声震于外。虽不能禁止。而于心不安。今宜详察礼文之意。勿令有所震动。若惧不坚固。则但令密杵而筑之。庶几两全。且礼文。下土每以尺许为准。此亦多用之。以俟其实之意。要须十分审察。不可全任役人所为也。
加详审。不敢以但欲坚固之故。使之震动柩中。余屡见人家葬事。自下灰未及尺许。而役夫踊跃筑杵。声震于外。虽不能禁止。而于心不安。今宜详察礼文之意。勿令有所震动。若惧不坚固。则但令密杵而筑之。庶几两全。且礼文。下土每以尺许为准。此亦多用之。以俟其实之意。要须十分审察。不可全任役人所为也。藏明器
家礼。以板塞其门。但恐板木既朽。则土有崩陷之患。以砖或石代之。似无此患。更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