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x 页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书状
书状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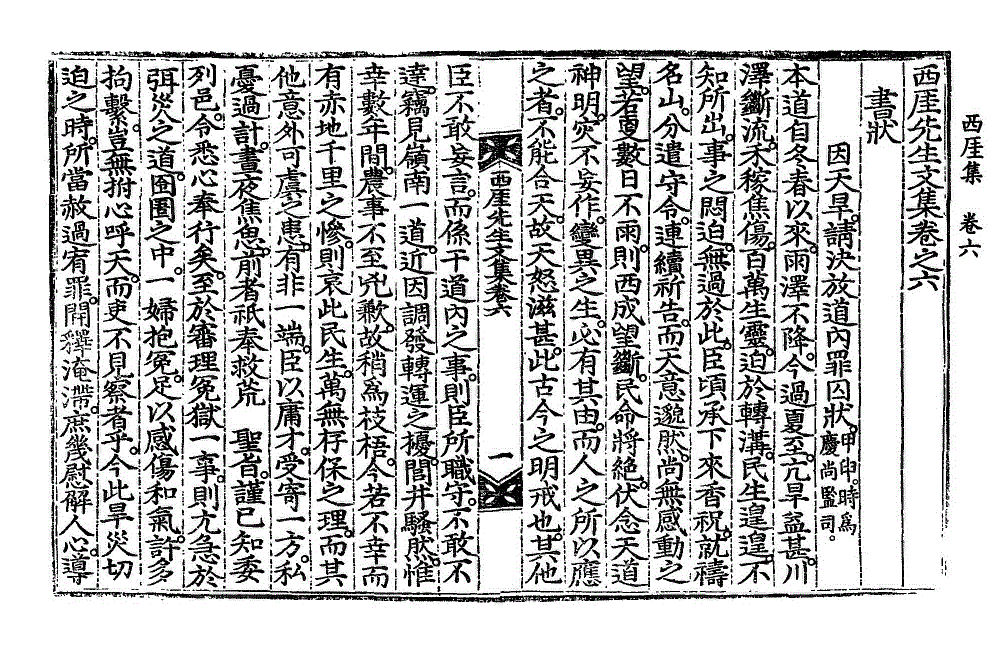 因天旱。请决放道内罪囚状。(甲申。时为庆尚监司。)
因天旱。请决放道内罪囚状。(甲申。时为庆尚监司。)本道自冬春以来。雨泽不降。今过夏至。亢旱益甚。川泽断流。禾稼焦伤。百万生灵。迫于转沟。民生遑遑。不知所出。事之闷迫。无过于此。臣顷承下来香祝。就祷名山。分遣守令。连续祈告。而天意邈然。尚无感动之望。若更数日不雨。则西成望断。民命将绝。伏念天道神明。灾不妄作。变异之生。必有其由。而人之所以应之者。不能合天。故天怒滋甚。此古今之明戒也。其他臣不敢妄言。而系干道内之事。则臣所职守。不敢不达。窃见岭南一道。近因调发转运之扰。闾井骚然。惟幸数年间。农事不至凶歉。故稍为枝梧。今若不幸而有赤地千里之惨。则哀此民生。万无存保之理。而其他意外可虞之患。有非一端。臣以庸才。受寄一方。私忧过计。昼夜焦思。前者祇奉救荒 圣旨。谨已知委列邑。令悉心奉行矣。至于审理冤狱一事。则尤急于弭灾之道。囹圄之中。一妇抱冤。足以感伤和气。许多拘系。岂无拊心呼天。而吏不见察者乎。今此旱灾切迫之时。所当赦过宥罪。开释淹滞。庶几慰解人心。导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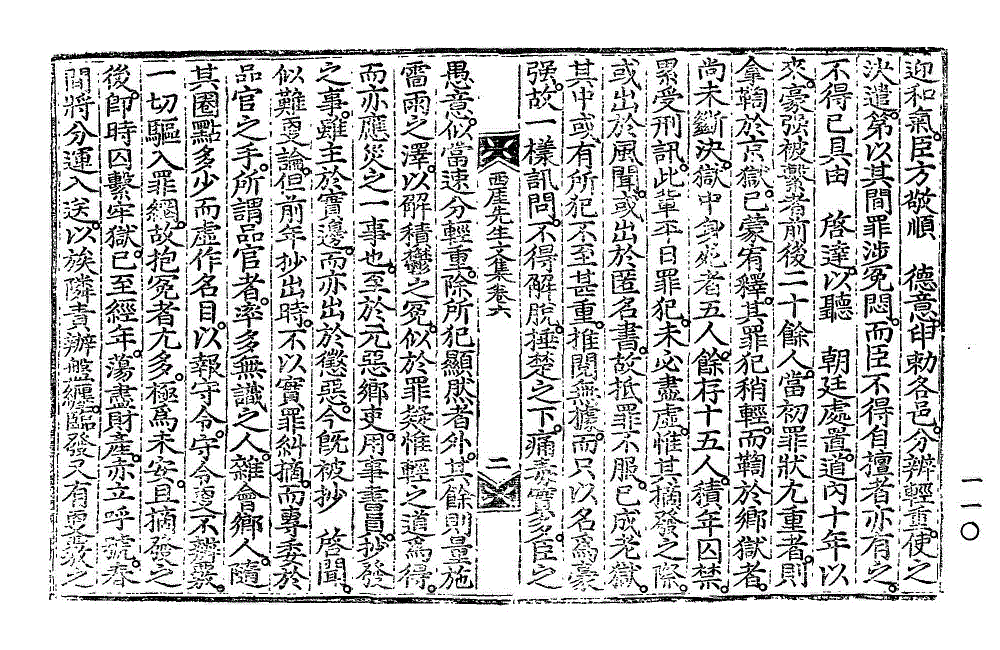 迎和气。臣方敬顺 德意。申敕各邑。分辨轻重。使之决遣。第以其间罪涉冤闷。而臣不得自擅者亦有之。不得已具由 启达。以听 朝廷处置。道内十年以来。豪强被系者前后二十馀人。当初罪状尤重者。则拿鞫于京狱。已蒙宥释。其罪犯稍轻。而鞫于乡狱者。尚未断决。狱中身死者五人。馀存十五人。绩年囚禁。累受刑讯。此辈平日罪犯。未必尽虚。惟其摘发之际。或出于风闻。或出于匿名书。故抵罪不服。已成老狱。其中或有所犯不至甚重。推阅无据。而只以名为豪强。故一样讯问。不得解脱。捶楚之下。痛毒实多。臣之愚意。似当速分轻重。除所犯显然者外。其馀则量施䨓雨之泽。以解积郁之冤。似于罪疑惟轻之道为得。而亦应灾之一事也。至于元恶乡吏。用事书员。抄发之事。虽主于实边。而亦出于惩恶。今既被抄 启闻。似难更论。但前年抄出时。不以实罪纠摘。而专委于品官之手。所谓品官者。率多无识之人。杂会乡人。随其圈点多少而虚作名目。以报守令。守令更不辨覈。一切驱入罪网。故抱冤者尤多。极为未安。且摘发之后。即时囚系牢狱。已至经年。荡尽财产。赤立呼号。春间将分运入送。以族邻责办盘缠。临发又有更覈之
迎和气。臣方敬顺 德意。申敕各邑。分辨轻重。使之决遣。第以其间罪涉冤闷。而臣不得自擅者亦有之。不得已具由 启达。以听 朝廷处置。道内十年以来。豪强被系者前后二十馀人。当初罪状尤重者。则拿鞫于京狱。已蒙宥释。其罪犯稍轻。而鞫于乡狱者。尚未断决。狱中身死者五人。馀存十五人。绩年囚禁。累受刑讯。此辈平日罪犯。未必尽虚。惟其摘发之际。或出于风闻。或出于匿名书。故抵罪不服。已成老狱。其中或有所犯不至甚重。推阅无据。而只以名为豪强。故一样讯问。不得解脱。捶楚之下。痛毒实多。臣之愚意。似当速分轻重。除所犯显然者外。其馀则量施䨓雨之泽。以解积郁之冤。似于罪疑惟轻之道为得。而亦应灾之一事也。至于元恶乡吏。用事书员。抄发之事。虽主于实边。而亦出于惩恶。今既被抄 启闻。似难更论。但前年抄出时。不以实罪纠摘。而专委于品官之手。所谓品官者。率多无识之人。杂会乡人。随其圈点多少而虚作名目。以报守令。守令更不辨覈。一切驱入罪网。故抱冤者尤多。极为未安。且摘发之后。即时囚系牢狱。已至经年。荡尽财产。赤立呼号。春间将分运入送。以族邻责办盘缠。临发又有更覈之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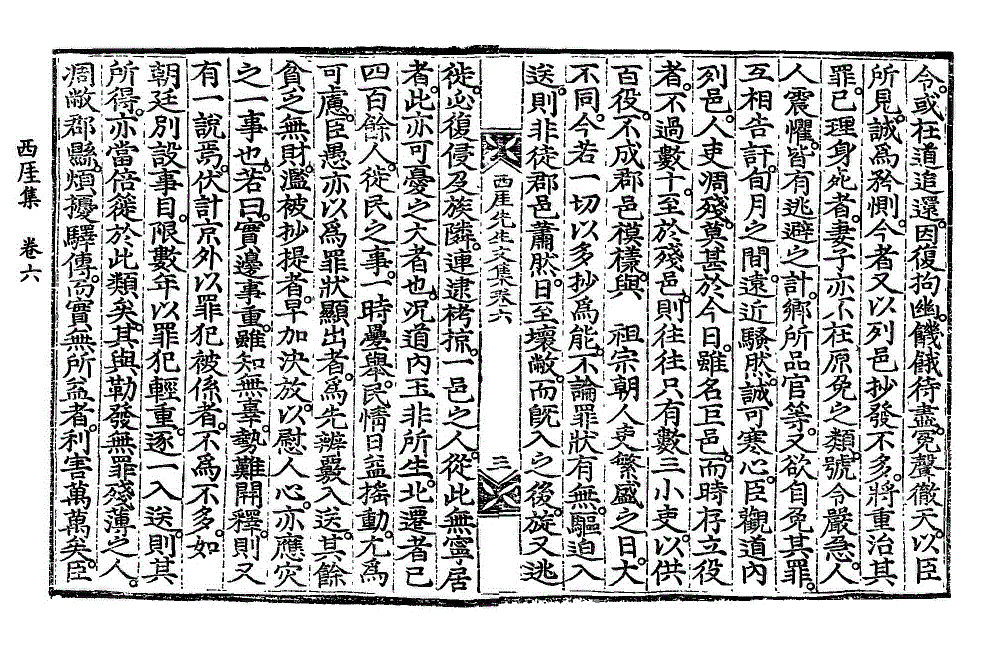 令。或在道追还。因复拘幽。饥饿待尽。冤声彻天。以臣所见。诚为矜恻。今者又以列邑抄发不多。将重治其罪。已理身死者。妻子亦不在原免之类。号令严急。人人震惧。皆有逃避之计。乡所品官等。又欲自免其罪。互相告讦。旬月之间。远近骚然。诚可寒心。臣观道内列邑。人吏凋残。莫甚于今日。虽名巨邑。而时存立役者。不过数十。至于残邑。则往往只有数三小吏。以供百役。不成郡邑模样。与 祖宗朝人吏繁盛之日。大不同。今若一切以多抄为能。不论罪状有无。驱迫入送。则非徒郡邑萧然。日至坏敝。而既入之后。旋又逃徙。必复侵及族邻。连逮栲掠。一邑之人。从此无宁居者。此亦可忧之大者也。况道内玉非所生。北迁者已四百馀人。徙民之事。一时叠举。民情日益摇动。尤为可虑。臣愚亦以为罪状显出者。为先辨覈入送。其馀贫乏无财。滥被抄提者。早加决放。以慰人心。亦应灾之一事也。若曰。实边事重。虽知无辜。势难开释。则又有一说焉。伏计京外以罪犯被系者。不为不多。如 朝廷别设事目。限数年以罪犯轻重。逐一入送。则其所得。亦当倍蓗于此类矣。其与勒发无罪残薄之人。凋敝郡县。烦扰驿传。而实无所益者。利害万万矣。臣
令。或在道追还。因复拘幽。饥饿待尽。冤声彻天。以臣所见。诚为矜恻。今者又以列邑抄发不多。将重治其罪。已理身死者。妻子亦不在原免之类。号令严急。人人震惧。皆有逃避之计。乡所品官等。又欲自免其罪。互相告讦。旬月之间。远近骚然。诚可寒心。臣观道内列邑。人吏凋残。莫甚于今日。虽名巨邑。而时存立役者。不过数十。至于残邑。则往往只有数三小吏。以供百役。不成郡邑模样。与 祖宗朝人吏繁盛之日。大不同。今若一切以多抄为能。不论罪状有无。驱迫入送。则非徒郡邑萧然。日至坏敝。而既入之后。旋又逃徙。必复侵及族邻。连逮栲掠。一邑之人。从此无宁居者。此亦可忧之大者也。况道内玉非所生。北迁者已四百馀人。徙民之事。一时叠举。民情日益摇动。尤为可虑。臣愚亦以为罪状显出者。为先辨覈入送。其馀贫乏无财。滥被抄提者。早加决放。以慰人心。亦应灾之一事也。若曰。实边事重。虽知无辜。势难开释。则又有一说焉。伏计京外以罪犯被系者。不为不多。如 朝廷别设事目。限数年以罪犯轻重。逐一入送。则其所得。亦当倍蓗于此类矣。其与勒发无罪残薄之人。凋敝郡县。烦扰驿传。而实无所益者。利害万万矣。臣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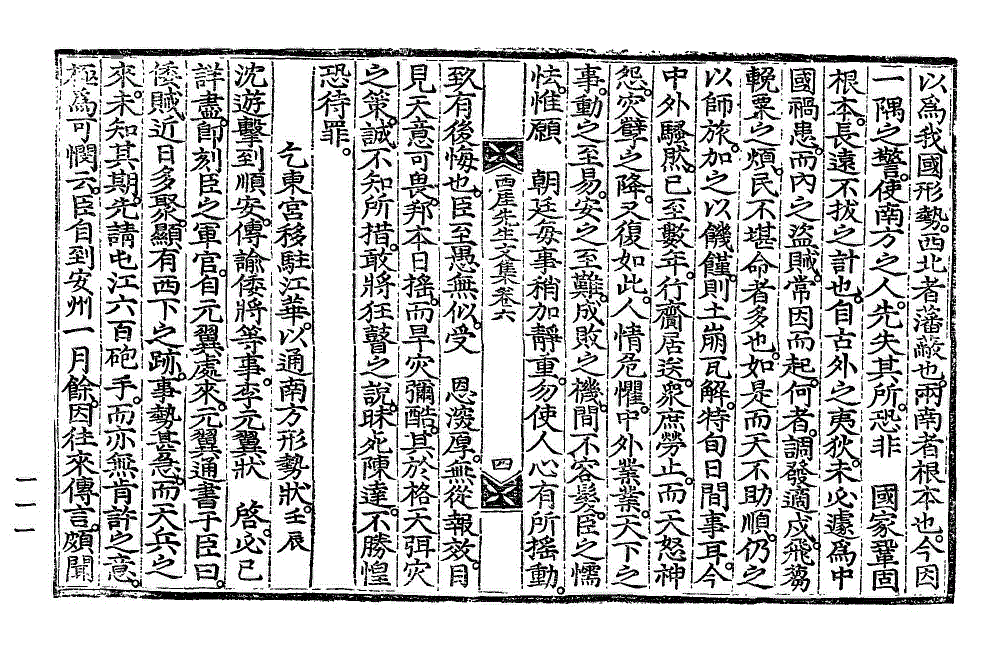 以为我国刑势。西北者藩蔽也。两南者根本也。今因一隅之警。使南方之人。先失其所。恐非 国家巩固根本。长远不拔之计也。自古外之夷狄。未必遽为中国祸患。而内之盗贼。常因而起。何者。调发适戍。飞刍挽粟之烦。民不堪命者多也。如是而天不助顺。仍之以师旅。加之以饥馑。则土崩瓦解。特旬日间事耳。今中外骚然。已至数年。行赍居送。众庶劳止。而天怒神怨。灾孽之降。又复如此。人情危惧。中外业业。天下之事。动之至易。安之至难。成败之机。间不容发。臣之懦怯。惟愿 朝廷每事稍加静重。勿使人心有所摇动。致有后悔也。臣至愚无似。受 恩深厚。无从报效。目见天意可畏。邦本日摇。而旱灾弥酷。其于格天弭灾之策。诚不知所措。敢将狂瞽之说。昧死陈达。不胜惶恐待罪。
以为我国刑势。西北者藩蔽也。两南者根本也。今因一隅之警。使南方之人。先失其所。恐非 国家巩固根本。长远不拔之计也。自古外之夷狄。未必遽为中国祸患。而内之盗贼。常因而起。何者。调发适戍。飞刍挽粟之烦。民不堪命者多也。如是而天不助顺。仍之以师旅。加之以饥馑。则土崩瓦解。特旬日间事耳。今中外骚然。已至数年。行赍居送。众庶劳止。而天怒神怨。灾孽之降。又复如此。人情危惧。中外业业。天下之事。动之至易。安之至难。成败之机。间不容发。臣之懦怯。惟愿 朝廷每事稍加静重。勿使人心有所摇动。致有后悔也。臣至愚无似。受 恩深厚。无从报效。目见天意可畏。邦本日摇。而旱灾弥酷。其于格天弭灾之策。诚不知所措。敢将狂瞽之说。昧死陈达。不胜惶恐待罪。乞东宫移驻江华。以通南方形势状。(壬辰)
沈游击到顺安。传谕倭将等事。李元翼状 启。必已详尽。即刻臣之军官。自元翼处来。元翼通书于臣曰。倭贼近日多聚。显有西下之迹。事势甚急。而天兵之来。未知其期。先请屯江六百炮手。而亦无肯许之意。极为可悯云。臣自到安州一月馀。因往来传言。颇闻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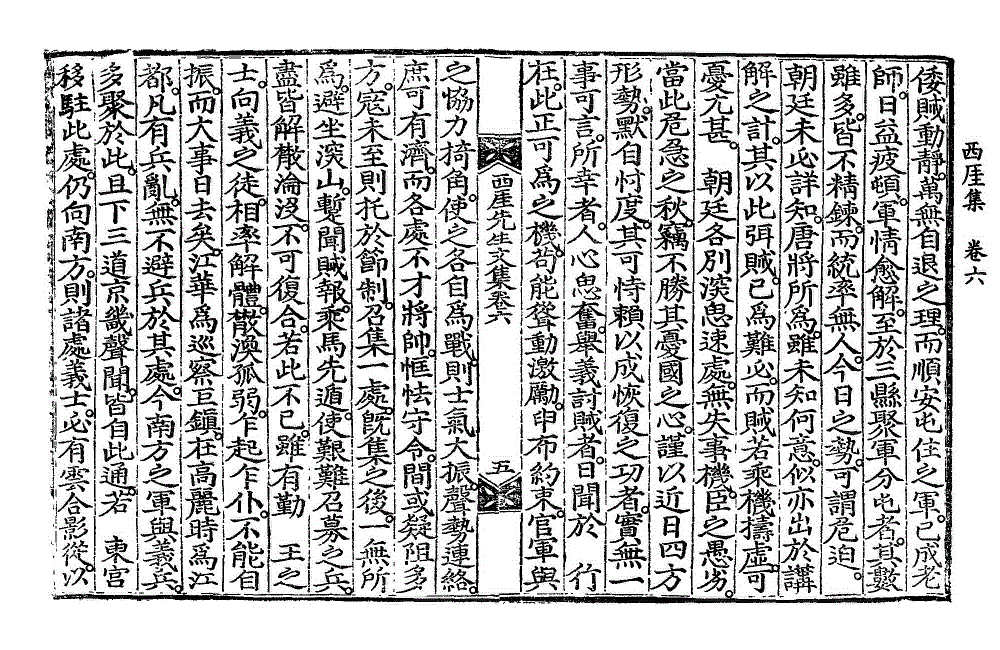 倭贼动静。万无自退之理。而顺安屯住之军。已成老师。日益疲顿。军情愈解。至于三县聚军分屯者。其数虽多。皆不精鍊。而统率无人。今日之势。可谓危迫。 朝廷未必详知。唐将所为。虽未知何意。似亦出于讲解之计。其以此弭贼。已为难必。而贼若乘机捣虚。可忧尤甚。 朝廷各别深思速处。无失事机。臣之愚劣。当此危急之秋。窃不胜其忧国之心。谨以近日四方形势。默自忖度。其可恃赖以成恢复之功者。实无一事可言。所幸者。人心思奋。举义讨贼者。日闻于 行在。此正可为之机。苟能耸动激励。申布约束。官军与之协力掎角。使之各自为战。则士气大振。声势连络。庶可有济。而各处不才将帅。恇怯守令。间或疑阻多方。寇未至则托于节制。召集一处。既集之后。一无所为。避坐深山。暂闻贼报。乘马先遁。使艰难召募之兵。尽皆解散沦没。不可复合。若此不已。虽有勤 王之士。向义之徒。相率解体。散涣孤弱。乍起乍仆。不能自振。而大事日去矣。江华为巡察巨镇。在高丽时为江都。凡有兵乱。无不避兵于其处。今南方之军与义兵。多聚于此。且下三道京畿声闻。皆自此通。若 东宫移驻此处。仍向南方。则诸处义士。必有云合影从。以
倭贼动静。万无自退之理。而顺安屯住之军。已成老师。日益疲顿。军情愈解。至于三县聚军分屯者。其数虽多。皆不精鍊。而统率无人。今日之势。可谓危迫。 朝廷未必详知。唐将所为。虽未知何意。似亦出于讲解之计。其以此弭贼。已为难必。而贼若乘机捣虚。可忧尤甚。 朝廷各别深思速处。无失事机。臣之愚劣。当此危急之秋。窃不胜其忧国之心。谨以近日四方形势。默自忖度。其可恃赖以成恢复之功者。实无一事可言。所幸者。人心思奋。举义讨贼者。日闻于 行在。此正可为之机。苟能耸动激励。申布约束。官军与之协力掎角。使之各自为战。则士气大振。声势连络。庶可有济。而各处不才将帅。恇怯守令。间或疑阻多方。寇未至则托于节制。召集一处。既集之后。一无所为。避坐深山。暂闻贼报。乘马先遁。使艰难召募之兵。尽皆解散沦没。不可复合。若此不已。虽有勤 王之士。向义之徒。相率解体。散涣孤弱。乍起乍仆。不能自振。而大事日去矣。江华为巡察巨镇。在高丽时为江都。凡有兵乱。无不避兵于其处。今南方之军与义兵。多聚于此。且下三道京畿声闻。皆自此通。若 东宫移驻此处。仍向南方。则诸处义士。必有云合影从。以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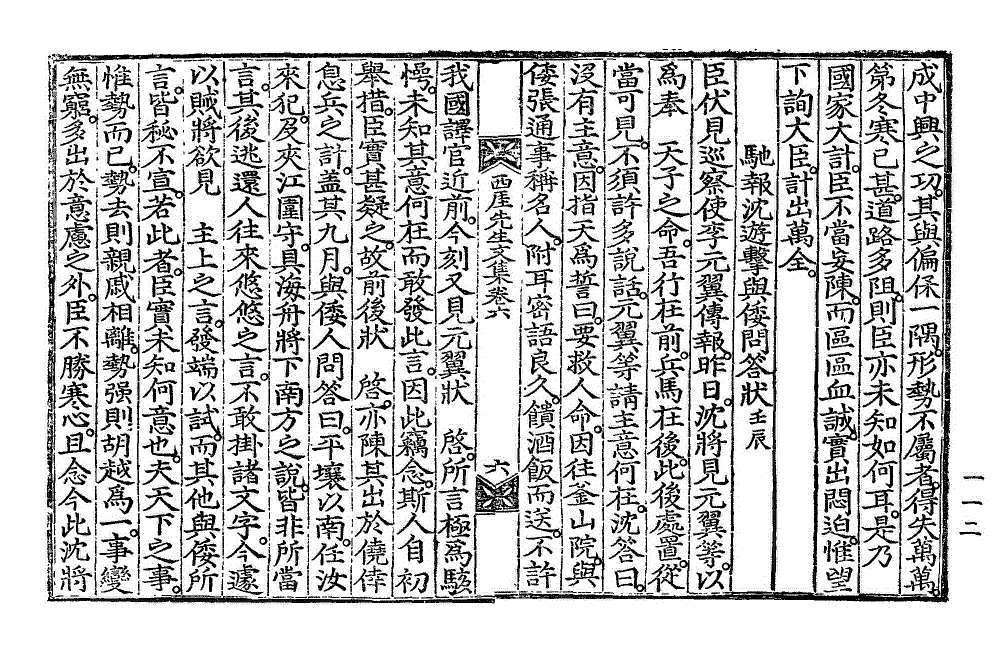 成中兴之功。其与偏保一隅。形势不属者。得失万万。第冬寒已甚。道路多阻。则臣亦未知如何耳。是乃 国家大计。臣不当妄陈。而区区血诚。实出闷迫。惟望下询大臣。计出万全。
成中兴之功。其与偏保一隅。形势不属者。得失万万。第冬寒已甚。道路多阻。则臣亦未知如何耳。是乃 国家大计。臣不当妄陈。而区区血诚。实出闷迫。惟望下询大臣。计出万全。驰报沈游击与倭问答状(壬辰)
臣伏见巡察使李元翼传报。昨日。沈将见元翼等。以为奉 天子之命。吾行在前。兵马在后。此后处置。从当可见。不须许多说话。元翼等请主意何在。沈答曰。没有主意。因指天为誓曰。要救人命。因往釜山院。与倭张通事称名人。附耳密语良久。馈酒饭而送。不许我国译官近前。今刻又见元翼状 启。所言极为骇愕。未知其意何在而敢发此言。因此窃念。斯人自初举措。臣实甚疑之。故前后状 启。亦陈其出于侥倖息兵之计。盖其九月。与倭人问答曰。平壤以南。任汝来犯。及夹江围守。具海舟将下南方之说。皆非所当言。其后逃还人往来悠悠之言。不敢挂诸文字。今遽以贼将欲见 主上之言。发端以试。而其他与倭所言。皆秘不宣。若此者。臣实未知何意也。夫天下之事。惟势而已。势去则亲戚相离。势强则胡越为一。事变无穷。多出于意虑之外。臣不胜寒心。且念今此沈将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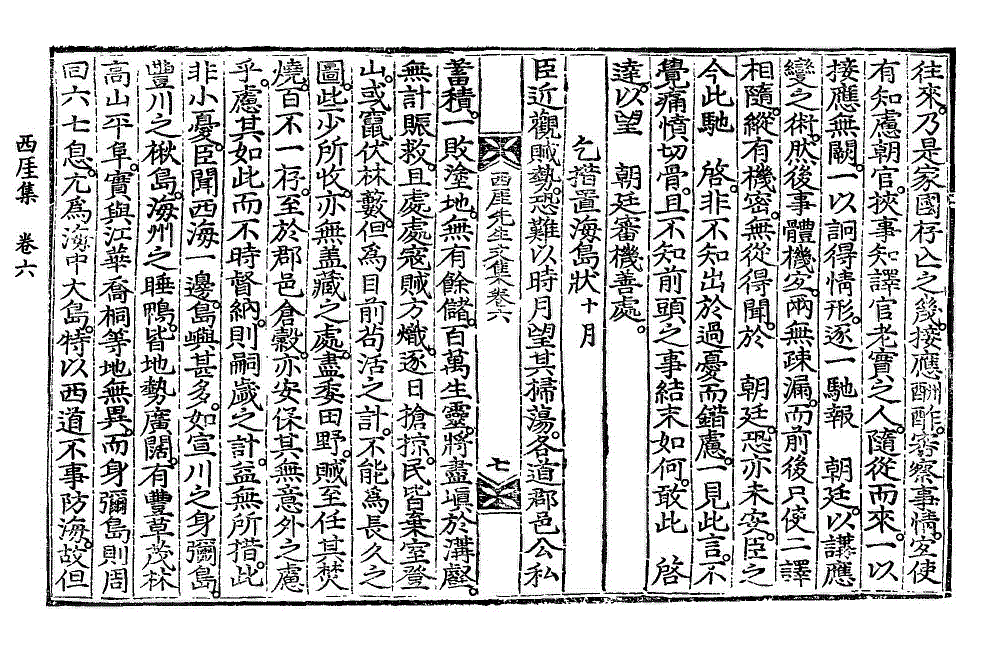 往来。乃是家国存亡之几。接应酬酢。审察事情。宜使有知虑朝官。挟事知译官老实之人。随从而来。一以接应无阙。一以诇得情形。逐一驰报 朝廷。以讲应变之术。然后事体机宜。两无疏漏。而前后只使二译相随。纵有机密。无从得闻。于 朝廷。恐亦未安。臣之今此驰 启。非不知出于过忧而错虑。一见此言。不觉痛愤切骨。且不知前头之事结末如何。敢此 启达。以望 朝廷审机善处。
往来。乃是家国存亡之几。接应酬酢。审察事情。宜使有知虑朝官。挟事知译官老实之人。随从而来。一以接应无阙。一以诇得情形。逐一驰报 朝廷。以讲应变之术。然后事体机宜。两无疏漏。而前后只使二译相随。纵有机密。无从得闻。于 朝廷。恐亦未安。臣之今此驰 启。非不知出于过忧而错虑。一见此言。不觉痛愤切骨。且不知前头之事结末如何。敢此 启达。以望 朝廷审机善处。乞措置海岛状(十月)
臣近观贼势。恐难以时月望其扫荡。各道郡邑公私蓄积。一败涂地。无有馀储。百万生灵。将尽填于沟壑。无计赈救。且处处寇贼方炽。逐日抢掠。民皆弃室登山。或窜伏林薮。但为目前苟活之计。不能为长久之图。些少所收。亦无盖藏之处。尽委田野。贼至任其焚烧。百不一存。至于郡邑仓谷。亦安保其无意外之虑乎。虑其如此而不时督纳。则嗣岁之计。益无所措。此非小忧。臣闻西海一边。岛屿甚多。如宣川之身弥岛。丰川之楸岛。海州之睡鸭。皆地势广阔。有丰草茂林高山平阜。实与江华乔桐等地无异。而身弥岛则周回六七息。尤为海中大岛。特以西道不事防海。故但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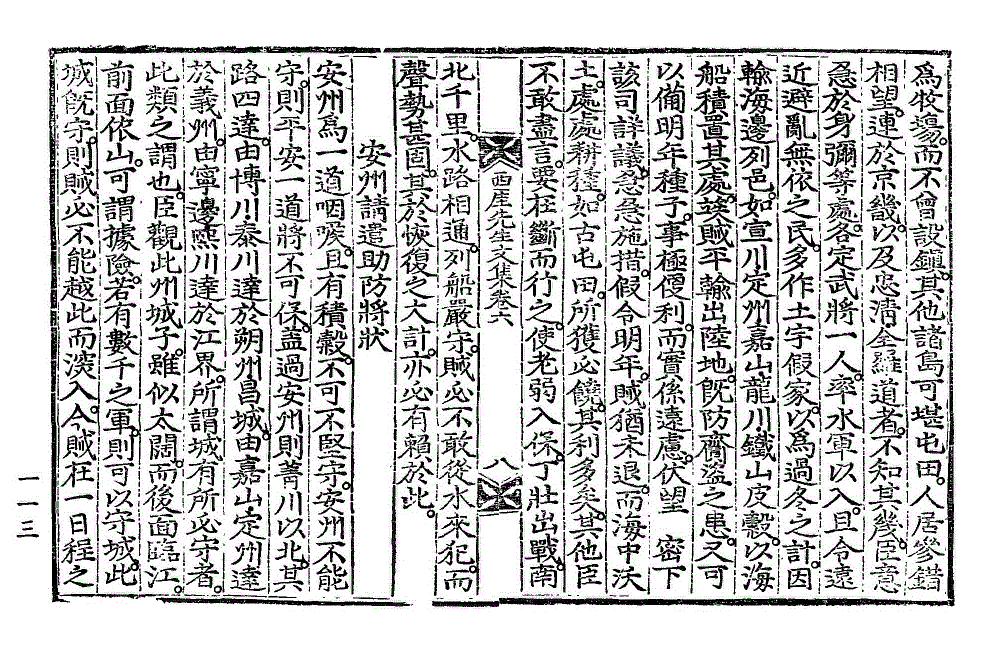 为牧场。而不曾设镇。其他诸岛可堪屯田。人居参错相望。连于京畿。以及忠清,全罗道者。不知其几。臣意急于身弥等处。各定武将一人。率水军以入。且令远近避乱无依之民。多作土宇假家。以为过冬之计。因输海边列邑。如宣川,定州,嘉山,龙川,铁山皮谷。以海船积置其处。俟贼平输出陆地。既防赍盗之患。又可以备明年种子。事极便利。而实系远虑。伏望 密下该司详议。急急施措。假令明年。贼犹未退。而海中沃土。处处耕种。如古屯田。所获必饶。其利多矣。其他臣不敢尽言。要在断而行之。使老弱入保。丁壮出战。南北千里。水路相通。列船严守。贼必不敢从水来犯。而声势甚固。其于恢复之大计。亦必有赖于此。
为牧场。而不曾设镇。其他诸岛可堪屯田。人居参错相望。连于京畿。以及忠清,全罗道者。不知其几。臣意急于身弥等处。各定武将一人。率水军以入。且令远近避乱无依之民。多作土宇假家。以为过冬之计。因输海边列邑。如宣川,定州,嘉山,龙川,铁山皮谷。以海船积置其处。俟贼平输出陆地。既防赍盗之患。又可以备明年种子。事极便利。而实系远虑。伏望 密下该司详议。急急施措。假令明年。贼犹未退。而海中沃土。处处耕种。如古屯田。所获必饶。其利多矣。其他臣不敢尽言。要在断而行之。使老弱入保。丁壮出战。南北千里。水路相通。列船严守。贼必不敢从水来犯。而声势甚固。其于恢复之大计。亦必有赖于此。安州请遣助防将状
安州为一道咽喉。且有积谷。不可不坚守。安州不能守。则平安一道将不可保。盖过安州则菁川以北。其路四达。由博川,泰川达于朔州,昌城。由嘉山,定州达于义州。由宁边,熙川达于江界。所谓城有所必守者。此类之谓也。臣观此州城子。虽似太阔。而后面临江。前面依山。可谓据险。若有数千之军。则可以守城。此城既守。则贼必不能越此而深入。今贼在一日程之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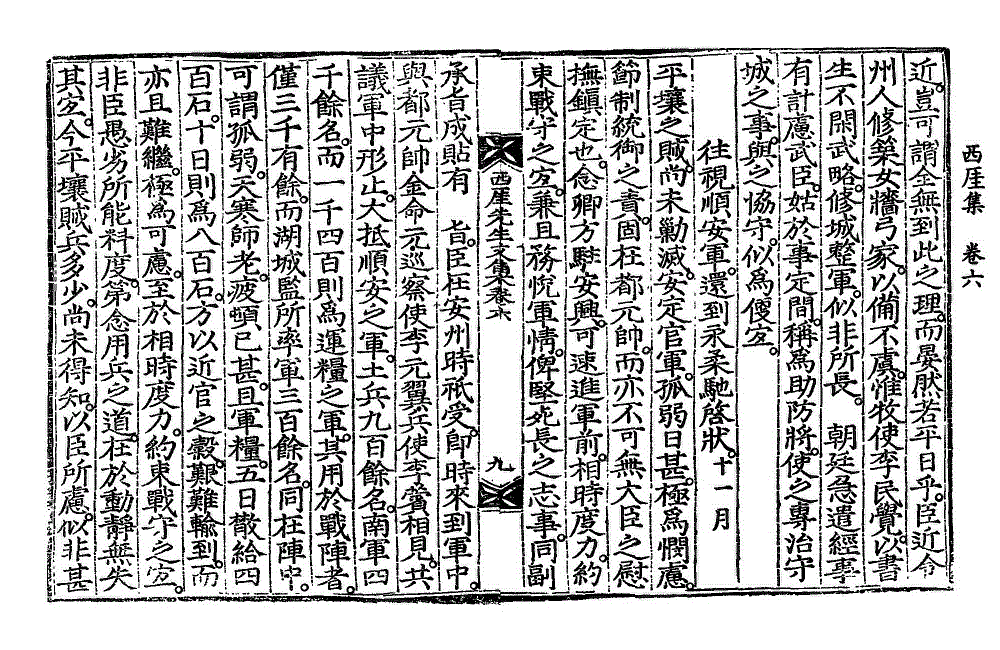 近。岂可谓全无到此之理。而晏然若平日乎。臣近令州人修筑女墙弓家。以备不虞。惟牧使李民觉。以书生不闲武略。修城整军。似非所长。 朝廷急遣经事有计虑武臣。姑于事定间。称为助防将。使之专治守城之事。与之协守。似为便宜。
近。岂可谓全无到此之理。而晏然若平日乎。臣近令州人修筑女墙弓家。以备不虞。惟牧使李民觉。以书生不闲武略。修城整军。似非所长。 朝廷急遣经事有计虑武臣。姑于事定间。称为助防将。使之专治守城之事。与之协守。似为便宜。往视顺安军。还到永柔驰启状。(十一月)
平壤之贼。尚未剿灭。安定官军。孤弱日甚。极为悯虑。节制统御之责。固在都元帅。而亦不可无大臣之慰抚镇定也。念卿方驻安兴。可速进军前。相时度力。约束战守之宜。兼且务悦军情。俾坚死长之志事。同副承旨成贴有 旨。臣在安州时祇受。即时来到军中。与都元帅金命元,巡察使李元翼,兵使李蘋相见。共议军中形止。大抵顺安之军。士兵九百馀名。南军四千馀名。而一千四百则为运粮之军。其用于战阵者。仅三千有馀。而湖城监所率军三百馀名。同在阵中。可谓孤弱。天寒师老。疲顿已甚。且军粮。五日散给四百石。十日则为八百石。方以近官之谷。艰难输到。而亦且难继。极为可虑。至于相时度力。约束战守之宜。非臣愚劣所能料度。第念用兵之道。在于动静无失其宜。今平壤贼兵多少。尚未得知。以臣所虑。似非甚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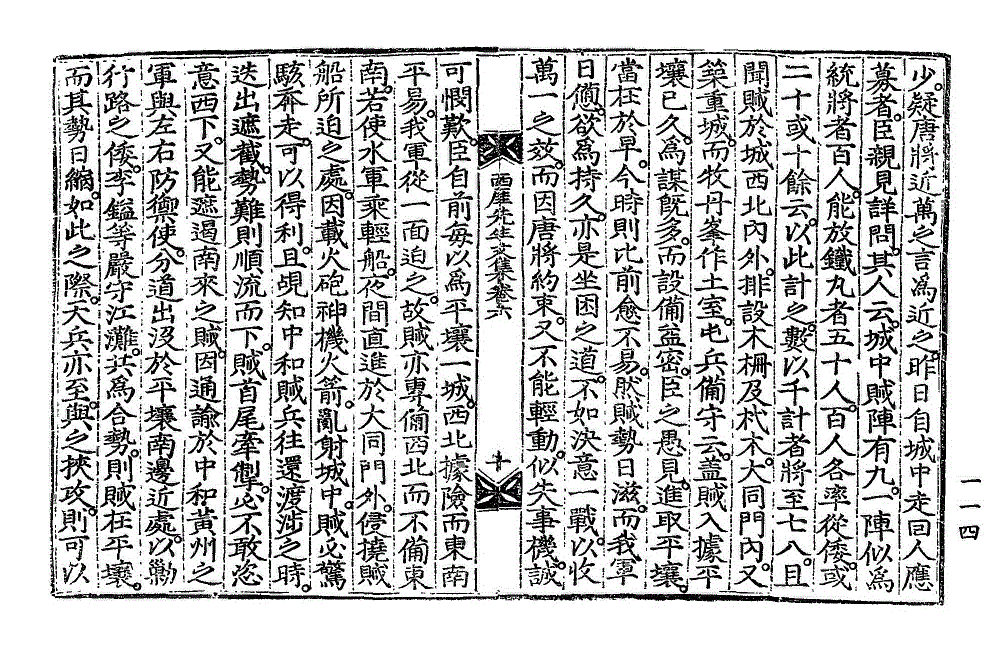 少。疑唐将近万之言为近之。昨日自城中走回人应募者。臣亲见详问。其人云。城中贼阵有九。一阵似为统将者百人。能放铁丸者五十人。百人各率从倭。或二十或十馀云。以此计之。数以千计者将至七八。且闻贼于城西北内外。排设木栅及杙木。大同门内。又筑重城。而牧丹峰作土室。屯兵备守云。盖贼入据平壤已久。为谋既多。而设备益密。臣之愚见。进取平壤。当在于早。今时则比前愈不易。然贼势日滋。而我军日惫。欲为持久。亦是坐困之道。不如决意一战。以收万一之效。而因唐将约束。又不能轻动。似失事机。诚可悯叹。臣自前每以为平壤一城。西北据险而东南平易。我军从一面迫之。故贼亦专备西北而不备东南。若使水军乘轻船。夜间直进于大同门外。侵挠贼船所迫之处。因载火炮神机火箭。乱射城中。贼必惊骇奔走。可以得利。且觇知中和贼兵往还渡涉之时。迭出遮截。势难则顺流而下。贼首尾牵掣。必不敢恣意西下。又能遮遏南来之贼。因通谕于中和,黄州之军与左右防御使。分道出没于平壤南边近处。以剿行路之倭。李镒等严守江滩。共为合势。则贼在平壤。而其势日缩。如此之际。天兵亦至。与之挟攻。则可以
少。疑唐将近万之言为近之。昨日自城中走回人应募者。臣亲见详问。其人云。城中贼阵有九。一阵似为统将者百人。能放铁丸者五十人。百人各率从倭。或二十或十馀云。以此计之。数以千计者将至七八。且闻贼于城西北内外。排设木栅及杙木。大同门内。又筑重城。而牧丹峰作土室。屯兵备守云。盖贼入据平壤已久。为谋既多。而设备益密。臣之愚见。进取平壤。当在于早。今时则比前愈不易。然贼势日滋。而我军日惫。欲为持久。亦是坐困之道。不如决意一战。以收万一之效。而因唐将约束。又不能轻动。似失事机。诚可悯叹。臣自前每以为平壤一城。西北据险而东南平易。我军从一面迫之。故贼亦专备西北而不备东南。若使水军乘轻船。夜间直进于大同门外。侵挠贼船所迫之处。因载火炮神机火箭。乱射城中。贼必惊骇奔走。可以得利。且觇知中和贼兵往还渡涉之时。迭出遮截。势难则顺流而下。贼首尾牵掣。必不敢恣意西下。又能遮遏南来之贼。因通谕于中和,黄州之军与左右防御使。分道出没于平壤南边近处。以剿行路之倭。李镒等严守江滩。共为合势。则贼在平壤。而其势日缩。如此之际。天兵亦至。与之挟攻。则可以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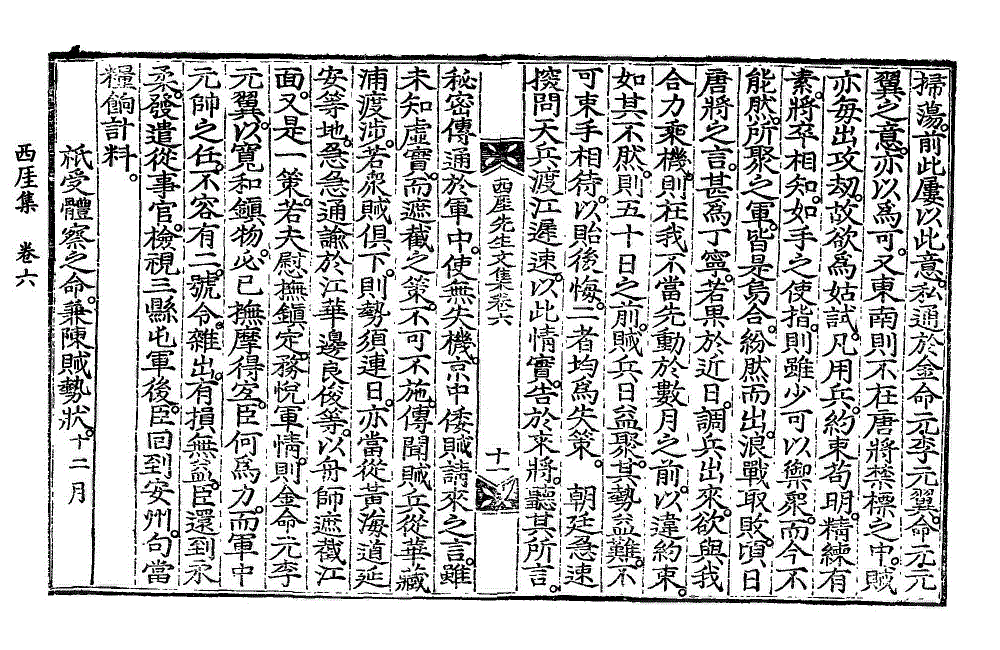 扫荡。前此屡以此意。私通于金命元,李元翼。命元,元翼之意。亦以为可。又东南则不在唐将禁标之中。贼亦每出攻劫。故欲为姑试。凡用兵。约束苟明。精练有素。将卒相知。如手之使指。则虽少可以御众。而今不能然。所聚之军。皆是乌合。纷然而出。浪战取败。顷日唐将之言。甚为丁宁。若果于近日。调兵出来。欲与我合力乘机。则在我不当先动于数月之前。以违约束。如其不然。则五十日之前。贼兵日益聚。其势益难。不可束手相待。以贻后悔。二者均为失策。 朝廷急速探问天兵渡江迟速。以此情实。告于来将。听其所言。秘密传通于军中。使无失机。京中倭贼请来之言。虽未知虚实。而遮截之策。不可不施。传闻贼兵从华藏浦渡涉。若众贼俱下。则势须连日。亦当从黄海道延安等地。急急通谕于江华边良俊等。以舟师遮截江面。又是一策。若夫慰抚镇定。务悦军情。则金命元李元翼。以宽和镇物。必已抚摩得宜。臣何为力。而军中元帅之任。不容有二。号令。杂出。有损无益。臣还到永柔。发遣从事官。检视三县屯军后。臣回到安州。句当粮饷计料。
扫荡。前此屡以此意。私通于金命元,李元翼。命元,元翼之意。亦以为可。又东南则不在唐将禁标之中。贼亦每出攻劫。故欲为姑试。凡用兵。约束苟明。精练有素。将卒相知。如手之使指。则虽少可以御众。而今不能然。所聚之军。皆是乌合。纷然而出。浪战取败。顷日唐将之言。甚为丁宁。若果于近日。调兵出来。欲与我合力乘机。则在我不当先动于数月之前。以违约束。如其不然。则五十日之前。贼兵日益聚。其势益难。不可束手相待。以贻后悔。二者均为失策。 朝廷急速探问天兵渡江迟速。以此情实。告于来将。听其所言。秘密传通于军中。使无失机。京中倭贼请来之言。虽未知虚实。而遮截之策。不可不施。传闻贼兵从华藏浦渡涉。若众贼俱下。则势须连日。亦当从黄海道延安等地。急急通谕于江华边良俊等。以舟师遮截江面。又是一策。若夫慰抚镇定。务悦军情。则金命元李元翼。以宽和镇物。必已抚摩得宜。臣何为力。而军中元帅之任。不容有二。号令。杂出。有损无益。臣还到永柔。发遣从事官。检视三县屯军后。臣回到安州。句当粮饷计料。祇受体察之命。兼陈贼势状。(十二月)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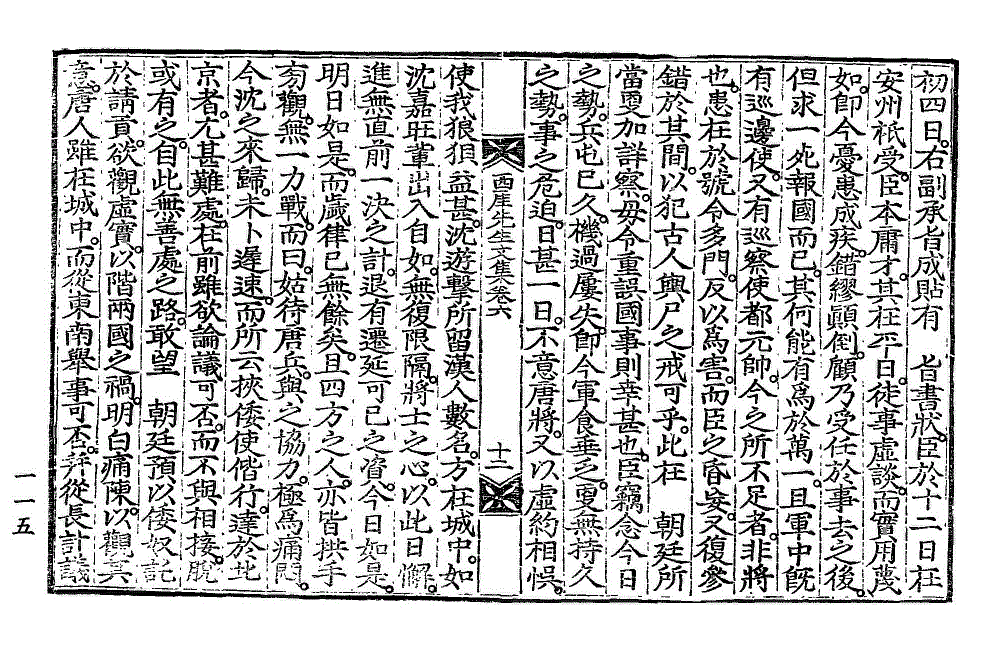 初四日。右副承旨成贴有 旨书状。臣于十二日在安州祇受。臣本庸才。其在平日。徒事虚谈。而实用蔑如。即今忧患成疾。错缪颠倒。顾乃受任于事去之后。但求一死报国而已。其何能有为于万一。且军中既有巡边使。又有巡察使都元帅。今之所不足者。非将也。患在于号令多门。反以为害。而臣之昏妄。又复参错于其间。以犯古人舆尸之戒可乎。此在 朝廷所当更加详察。毋令重误国事则幸甚也。臣窃念今日之势。兵屯已久。机过屡失。即今军食垂之。更无持久之势。事之危迫。日甚一日。不意唐将。又以虚约相误。使我狼狈益甚。沈游击所留汉人数名。方在城中。如沈嘉旺辈出入自如。无复限隔。将士之心。以此日懈。进无直前一决之计。退有迁延可已之资。今日如是。明日如是。而岁律已无馀矣。且四方之人。亦皆拱手旁观。无一力战。而曰。姑待唐兵。与之协力。极为痛闷。今沈之来归。未卜迟速。而所云挟倭使偕行。达于北京者。尤甚难处。在前虽欲论议可否。而不与相接。脱或有之。自此无善处之路。敢望 朝廷预以倭奴托于请贡。欲观虚实。以阶两国之祸。明白痛陈。以观其意。唐人虽在城中。而从东南举事可否。并从长计议
初四日。右副承旨成贴有 旨书状。臣于十二日在安州祇受。臣本庸才。其在平日。徒事虚谈。而实用蔑如。即今忧患成疾。错缪颠倒。顾乃受任于事去之后。但求一死报国而已。其何能有为于万一。且军中既有巡边使。又有巡察使都元帅。今之所不足者。非将也。患在于号令多门。反以为害。而臣之昏妄。又复参错于其间。以犯古人舆尸之戒可乎。此在 朝廷所当更加详察。毋令重误国事则幸甚也。臣窃念今日之势。兵屯已久。机过屡失。即今军食垂之。更无持久之势。事之危迫。日甚一日。不意唐将。又以虚约相误。使我狼狈益甚。沈游击所留汉人数名。方在城中。如沈嘉旺辈出入自如。无复限隔。将士之心。以此日懈。进无直前一决之计。退有迁延可已之资。今日如是。明日如是。而岁律已无馀矣。且四方之人。亦皆拱手旁观。无一力战。而曰。姑待唐兵。与之协力。极为痛闷。今沈之来归。未卜迟速。而所云挟倭使偕行。达于北京者。尤甚难处。在前虽欲论议可否。而不与相接。脱或有之。自此无善处之路。敢望 朝廷预以倭奴托于请贡。欲观虚实。以阶两国之祸。明白痛陈。以观其意。唐人虽在城中。而从东南举事可否。并从长计议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16H 页
 停当。驰谕于元帅及主兵之处。
停当。驰谕于元帅及主兵之处。论沈游击与贼讲解状
臣昨自肃川还安州。夜中见金命元通示状启草。末端语意。似未分明。大槩以臣所料。倭贼必不容易出去。而沈入城已累月。迄无一人来报消息。此亦极为可忧。贼气方骄。如未满其意。岂以一纸空文。遽为从命乎。况 中朝虽有此言。而不得我国之言。其势必有所要。沈之此计。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持和战并用之策。自投虎狼之口。其谋甚疏。而其势极危。假使万分有一贼佯为退去。以观如何。而挟沈偕行。大兵未集。江冰连陆。箕城新复之后。守备未完。亦难遽为鏖剿。其间事势狼狈。果如命元所虑。未知何以处之。 朝廷十分精思指挥。
论李镒代李蘋事未便宜状
臣在安州。传闻唐将率兵将至。虑一路凡事。或有疏缓。欲亲自点检。今到定州。适逢司谏李幼澄。暂闻 朝廷欲以李镒代李蘋。又以李荐代李镒为左防御使。 庙算所在。必非偶然。而以臣愚见。颇未稳洽。不敢不达。镒于诸将中。固有名称。近日治军料敌。亦颇可观。其欲代蘋。必有其意。若早为之。固无不可。今则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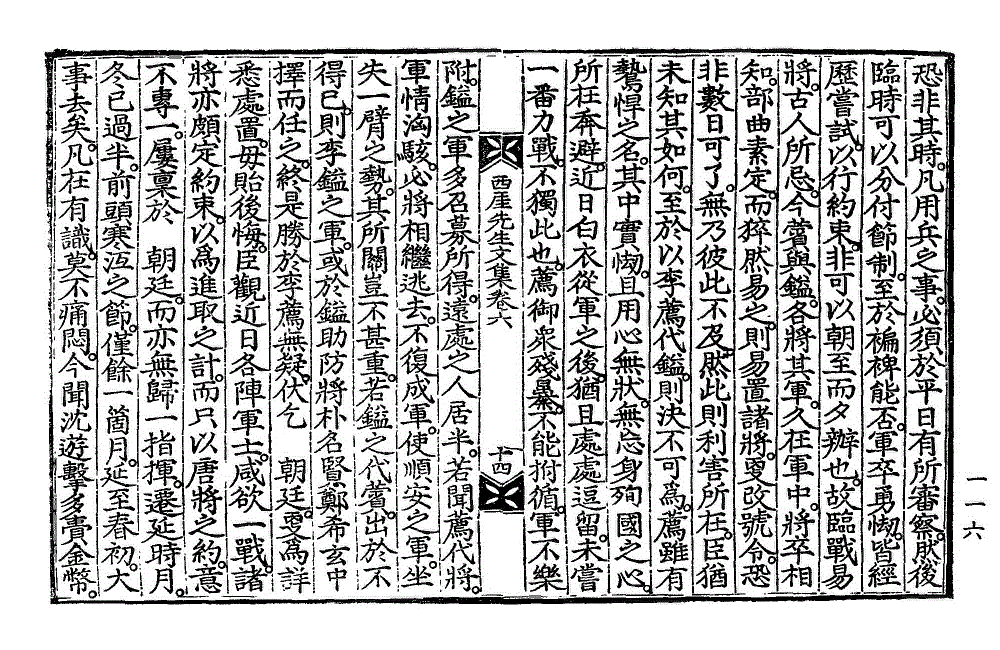 恐非其时。凡用兵之事。必须于平日有所审察。然后临时可以分付节制。至于褊裨能否。军卒勇㥘。皆经历尝试。以行约束。非可以朝至而夕办也。故临战易将。古人所忌。今蘋与镒。各将其军。久在军中。将卒相知。部曲素定。而猝然易之。则易置诸将。更改号令。恐非数日可了。无乃彼此不及。然此则利害所在。臣犹未知其如何。至于以李荐代镒。则决不可为。荐虽有鸷悍之名。其中实㥘。且用心无状。无忘身殉国之心。所在奔避。近日白衣从军之后。犹且处处逗留。未尝一番力战。不独此也。荐御众残暴。不能拊循。军不乐附。镒之军多召募所得。远处之人居半。若闻荐代将。军情汹骇。必将相继逃去。不复成军。使顺安之军。坐失一臂之势。其所关岂不甚重。若镒之代蘋。出于不得已。则李镒之军。或于镒助防将朴名贤,郑希玄中择而任之。终是胜于李荐无疑。伏乞 朝廷。更为详悉处置。毋贻后悔。臣观近日各阵军士。咸欲一战。诸将亦颇定约束。以为进取之计。而只以唐将之约。意不专一。屡禀于 朝廷。而亦无归一指挥。迁廷时月。冬已过半。前头寒冱之节。仅馀一个月。延至春初。大事去矣。凡在有识。莫不痛闷。今闻沈游击多赍金币。
恐非其时。凡用兵之事。必须于平日有所审察。然后临时可以分付节制。至于褊裨能否。军卒勇㥘。皆经历尝试。以行约束。非可以朝至而夕办也。故临战易将。古人所忌。今蘋与镒。各将其军。久在军中。将卒相知。部曲素定。而猝然易之。则易置诸将。更改号令。恐非数日可了。无乃彼此不及。然此则利害所在。臣犹未知其如何。至于以李荐代镒。则决不可为。荐虽有鸷悍之名。其中实㥘。且用心无状。无忘身殉国之心。所在奔避。近日白衣从军之后。犹且处处逗留。未尝一番力战。不独此也。荐御众残暴。不能拊循。军不乐附。镒之军多召募所得。远处之人居半。若闻荐代将。军情汹骇。必将相继逃去。不复成军。使顺安之军。坐失一臂之势。其所关岂不甚重。若镒之代蘋。出于不得已。则李镒之军。或于镒助防将朴名贤,郑希玄中择而任之。终是胜于李荐无疑。伏乞 朝廷。更为详悉处置。毋贻后悔。臣观近日各阵军士。咸欲一战。诸将亦颇定约束。以为进取之计。而只以唐将之约。意不专一。屡禀于 朝廷。而亦无归一指挥。迁廷时月。冬已过半。前头寒冱之节。仅馀一个月。延至春初。大事去矣。凡在有识。莫不痛闷。今闻沈游击多赍金币。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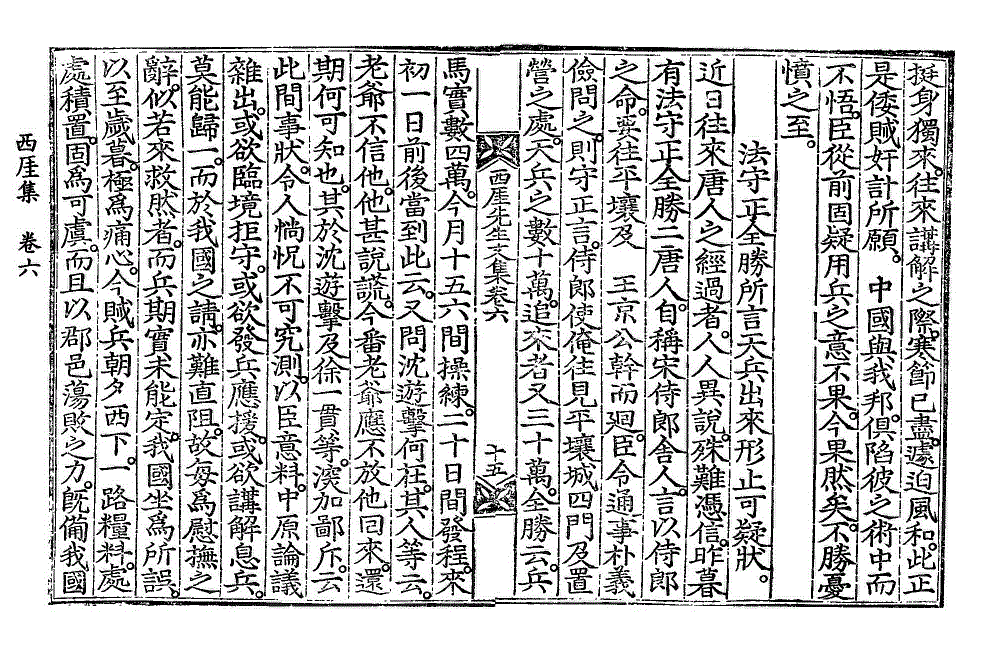 挺身独来。往来讲解之际。寒节已尽。遽迫风和。此正是倭贼奸计所愿。 中国与我邦。俱陷彼之术中而不悟。臣从前固疑用兵之意不果。今果然矣。不胜忧愤之至。
挺身独来。往来讲解之际。寒节已尽。遽迫风和。此正是倭贼奸计所愿。 中国与我邦。俱陷彼之术中而不悟。臣从前固疑用兵之意不果。今果然矣。不胜忧愤之至。法守正,全胜所言天兵出来形止可疑状。
近日往来唐人之经过者。人人异说。殊难凭信。昨暮有法守正,全胜二唐人。自称宋侍郎舍人。言以侍郎之命。要往平壤及 王京公干而回。臣令通事朴义俭问之。则守正言。侍郎使俺往见平壤城四门及置营之处。天兵之数十万。追来者又三十万。全胜云。兵马实数四万。今月十五六间操练。二十日间发程。来初一日前后当到此云。又问沈游击何在。其人等云。老爷不信他。他甚说谎。今番老爷应不放他回来。还期何可知也。其于沈游击及徐一贯等。深加鄙斥。云此间事状。令人惝恍不可究测。以臣意料。中原论议杂出。或欲临境拒守。或欲发兵应援。或欲讲解息兵。莫能归一。而于我国之请。亦难直阻。故每为慰抚之辞。似若来救然者。而兵期实未能定。我国坐为所误。以至岁暮。极为痛心。今贼兵朝夕西下。一路粮料。处处积置。固为可虞。而且以郡邑荡败之力。既备我国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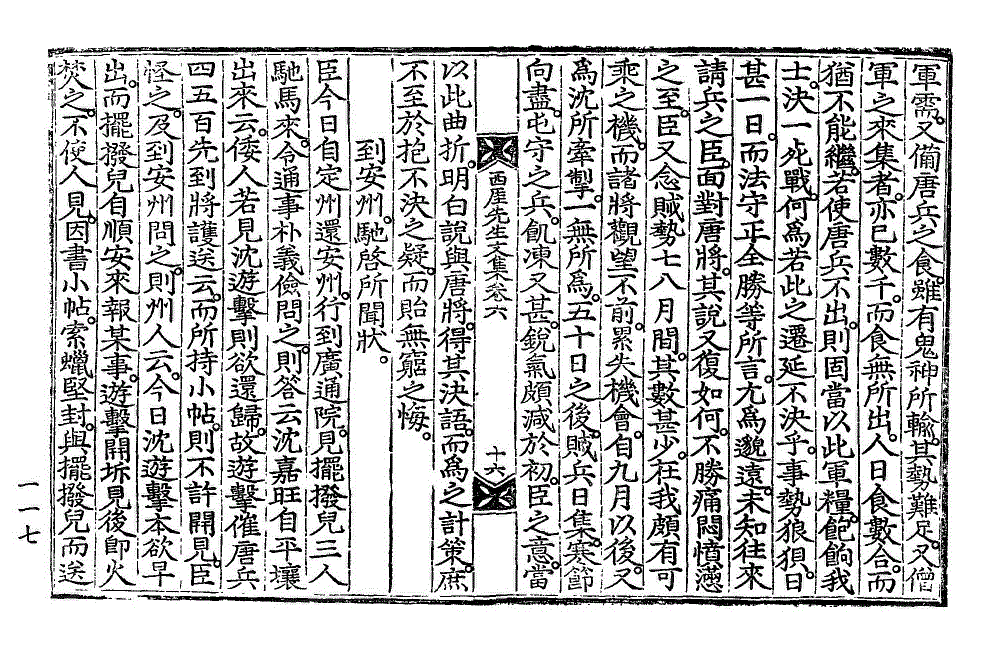 军需。又备唐兵之食。虽有鬼神所输。其势难足。又僧军之来集者。亦已数千。而食无所出。人日食数合。而犹不能继。若使唐兵不出。则固当以此军粮。饱饷我士。决一死战。何为若此之迁延不决乎。事势狼狈。日甚一日。而法守正,全胜等所言。尤为邈远。未知往来请兵之臣。面对唐将。其说又复如何。不胜痛闷愤懑之至。臣又念贼势七八月间。其数甚少。在我颇有可乘之机。而诸将观望不前。累失机会。自九月以后。又为沈所牵掣。一无所为。五十日之后。贼兵日集。寒节向尽。屯守之兵。饥冻又甚。锐气颇减于初。臣之意。当以此曲折。明白说与唐将。得其决语。而为之计策。庶不至于抱不决之疑。而贻无穷之悔。
军需。又备唐兵之食。虽有鬼神所输。其势难足。又僧军之来集者。亦已数千。而食无所出。人日食数合。而犹不能继。若使唐兵不出。则固当以此军粮。饱饷我士。决一死战。何为若此之迁延不决乎。事势狼狈。日甚一日。而法守正,全胜等所言。尤为邈远。未知往来请兵之臣。面对唐将。其说又复如何。不胜痛闷愤懑之至。臣又念贼势七八月间。其数甚少。在我颇有可乘之机。而诸将观望不前。累失机会。自九月以后。又为沈所牵掣。一无所为。五十日之后。贼兵日集。寒节向尽。屯守之兵。饥冻又甚。锐气颇减于初。臣之意。当以此曲折。明白说与唐将。得其决语。而为之计策。庶不至于抱不决之疑。而贻无穷之悔。到安州。驰启所闻状。
臣今日自定州还安州。行到广通院。见摆拨儿三人驰马来。令通事朴义俭问之。则答云沈嘉旺自平壤出来云。倭人若见沈游击则欲还归。故游击催唐兵四五百先到将护送云。而所持小帖。则不许开见。臣怪之。及到安州问之。则州人云。今日沈游击本欲早出。而摆拨儿自顺安来报某事。游击开坼见后即火焚之。不使人见。因书小帖。索蜡坚封。与摆拨儿而送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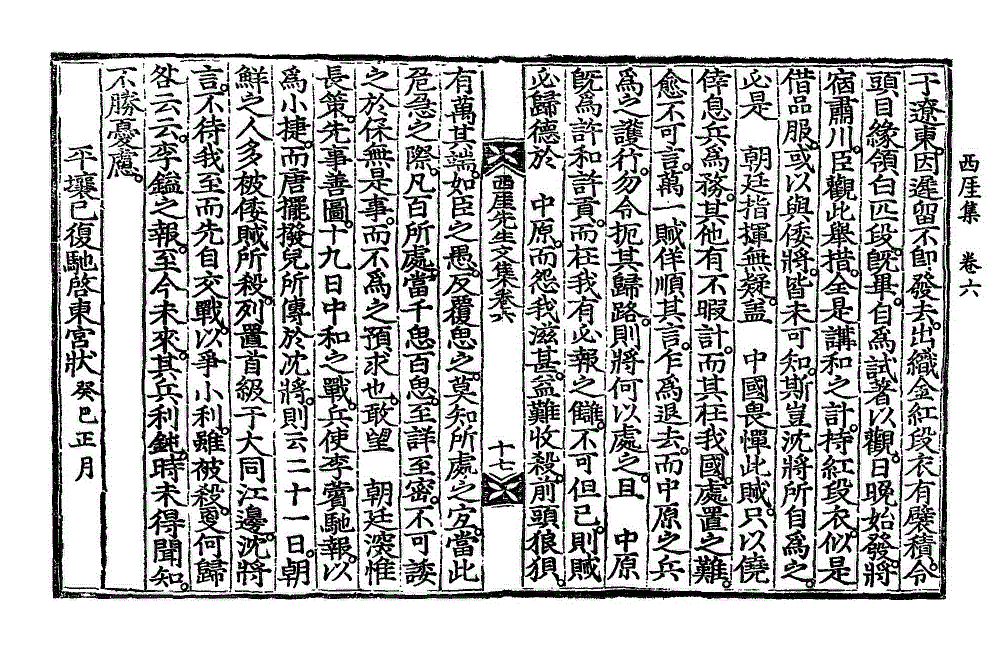 于辽东。因迟留不即发去。出织金红段衣有襞积。令头目缘领白匹段。既毕。自为试著以观。日晚始发。将宿肃川。臣观此举措。全是讲和之计。持红段衣。似是借品服。或以与倭将。皆未可知。斯岂沈将所自为之。必是 朝廷指挥无疑。盖 中国畏惮此贼。只以侥倖息兵为务。其他有不暇计。而其在我国。处置之难。愈不可言。万一贼佯顺其言。乍为退去。而中原之兵为之护行。勿令扼其归路。则将何以处之。且 中原既为许和许贡。而在我有必报之雠。不可但已。则贼必归德于 中原。而怨我滋甚。益难收杀。前头狼狈。有万其端。如臣之愚。反覆思之。莫知所处之宜。当此危急之际。凡百所处。当千思百思。至详至密。不可诿之于保无是事。而不为之预求也。敢望 朝廷深惟长策。先事善图。十九日中和之战。兵使李蘋驰报。以为小捷。而唐摆拨儿所传于沈将。则云二十一日。朝鲜之人多被倭贼所杀。列置首级于大同江边。沈将言。不待我至而先自交战。以争小利。虽被杀。更何归咎云云。李镒之报。至今未来。其兵利钝。时未得闻知。不胜忧虑。
于辽东。因迟留不即发去。出织金红段衣有襞积。令头目缘领白匹段。既毕。自为试著以观。日晚始发。将宿肃川。臣观此举措。全是讲和之计。持红段衣。似是借品服。或以与倭将。皆未可知。斯岂沈将所自为之。必是 朝廷指挥无疑。盖 中国畏惮此贼。只以侥倖息兵为务。其他有不暇计。而其在我国。处置之难。愈不可言。万一贼佯顺其言。乍为退去。而中原之兵为之护行。勿令扼其归路。则将何以处之。且 中原既为许和许贡。而在我有必报之雠。不可但已。则贼必归德于 中原。而怨我滋甚。益难收杀。前头狼狈。有万其端。如臣之愚。反覆思之。莫知所处之宜。当此危急之际。凡百所处。当千思百思。至详至密。不可诿之于保无是事。而不为之预求也。敢望 朝廷深惟长策。先事善图。十九日中和之战。兵使李蘋驰报。以为小捷。而唐摆拨儿所传于沈将。则云二十一日。朝鲜之人多被倭贼所杀。列置首级于大同江边。沈将言。不待我至而先自交战。以争小利。虽被杀。更何归咎云云。李镒之报。至今未来。其兵利钝。时未得闻知。不胜忧虑。平壤已复驰启东宫状(癸巳正月)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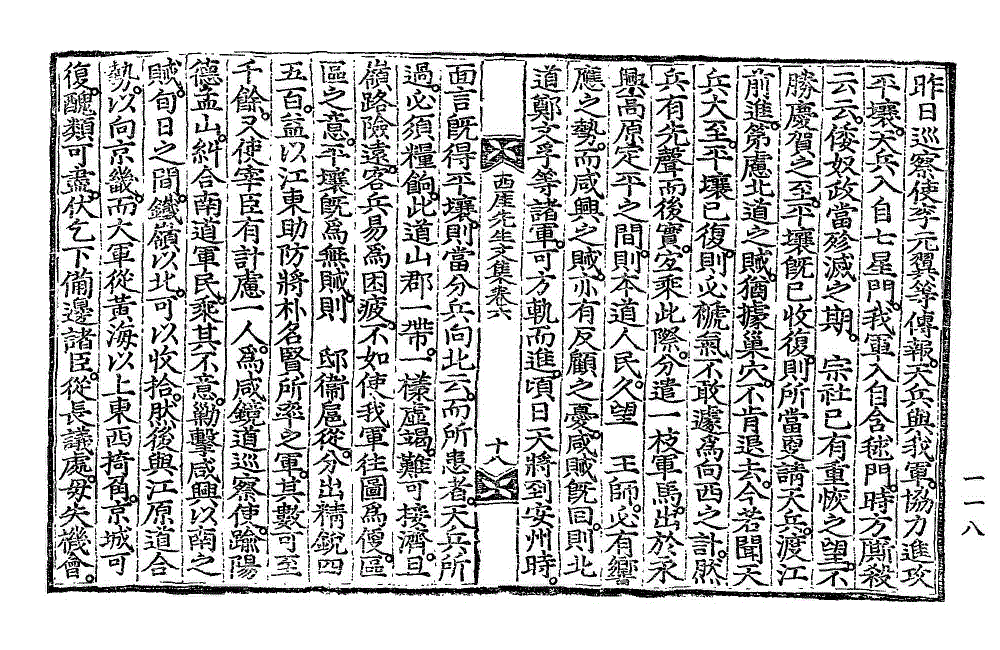 昨日巡察使李元翼等传报。天兵与我军。协力进攻平壤。天兵入自七星门。我军入自含毬门。时方厮杀云云。倭奴政当殄灭之期。 宗社已有重恢之望。不胜庆贺之至。平壤既已收复。则所当更请天兵。渡江前进。第虑北道之贼。犹据巢穴。不肯退去。今若闻天兵大至。平壤已复。则必褫气不敢遽为向西之计。然兵有先声而后实。宜乘此际。分遣一枝军马。出于永兴,高原,定平之间。则本道人民。久望 王师。必有响应之势。而咸兴之贼。亦有反顾之忧。咸贼既回。则北道郑文孚等诸军。可方轨而进。顷日天将到安州时。面言既得平壤。则当分兵向北云。而所患者。天兵所过。必须粮饷。此道山郡一带。一样虚竭。难可接济。且岭路险远。客兵易为因疲。不如使我军往图为便。区区之意。平壤既为无贼。则 邸卫扈从。分出精锐四五百。益以江东助防将朴名贤所率之军。其数可至千馀。又使宰臣有计虑一人。为咸镜道巡察使。踰阳德,孟山。纠合南道军民。乘其不意。剿击咸兴以南之贼。旬日之间。铁岭以北。可以收拾。然后与江原道合势。以向京畿。而大军从黄海以上东西掎角。京城可复。丑类可尽。伏乞下备边诸臣。从长议处。毋失机会。
昨日巡察使李元翼等传报。天兵与我军。协力进攻平壤。天兵入自七星门。我军入自含毬门。时方厮杀云云。倭奴政当殄灭之期。 宗社已有重恢之望。不胜庆贺之至。平壤既已收复。则所当更请天兵。渡江前进。第虑北道之贼。犹据巢穴。不肯退去。今若闻天兵大至。平壤已复。则必褫气不敢遽为向西之计。然兵有先声而后实。宜乘此际。分遣一枝军马。出于永兴,高原,定平之间。则本道人民。久望 王师。必有响应之势。而咸兴之贼。亦有反顾之忧。咸贼既回。则北道郑文孚等诸军。可方轨而进。顷日天将到安州时。面言既得平壤。则当分兵向北云。而所患者。天兵所过。必须粮饷。此道山郡一带。一样虚竭。难可接济。且岭路险远。客兵易为因疲。不如使我军往图为便。区区之意。平壤既为无贼。则 邸卫扈从。分出精锐四五百。益以江东助防将朴名贤所率之军。其数可至千馀。又使宰臣有计虑一人。为咸镜道巡察使。踰阳德,孟山。纠合南道军民。乘其不意。剿击咸兴以南之贼。旬日之间。铁岭以北。可以收拾。然后与江原道合势。以向京畿。而大军从黄海以上东西掎角。京城可复。丑类可尽。伏乞下备边诸臣。从长议处。毋失机会。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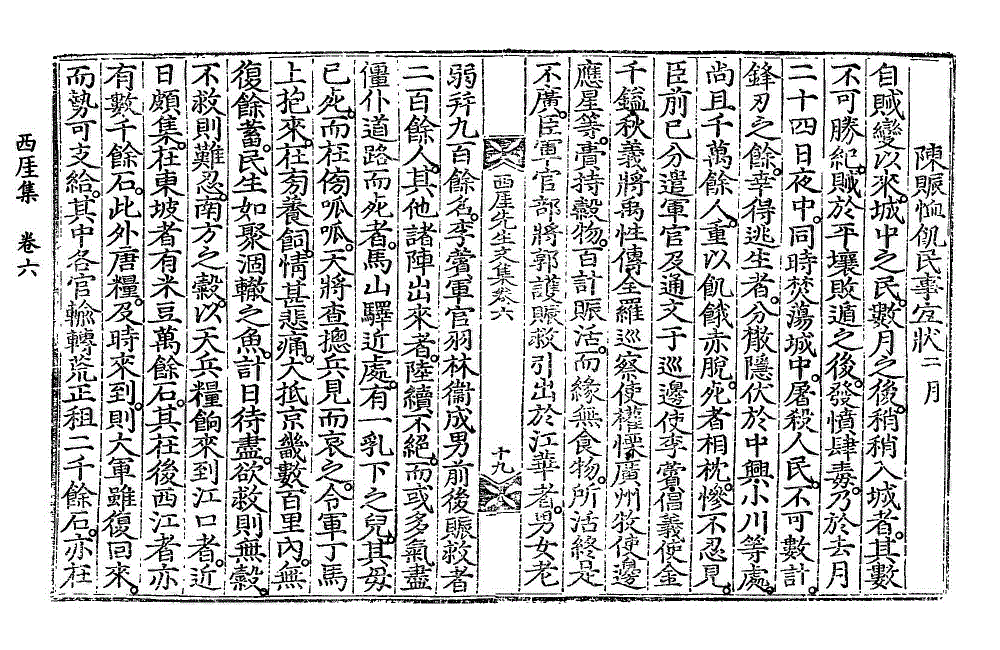 陈赈恤饥民事宜状(二月)
陈赈恤饥民事宜状(二月)自贼变以来。城中之民。数月之后。稍稍入城者。其数不可胜纪。贼于平壤败遁之后。发愤肆毒。乃于去月二十四日夜中。同时焚荡城中。屠杀人民。不可数计。锋刃之馀。幸得逃生者。分散隐伏于中兴,小川等处。尚且千万馀人。重以饥饿赤脱。死者相枕。惨不忍见。臣前已分遣军官及通文于巡边使李蘋,倡义使金千镒,秋义将禹性传,全罗巡察使权慄,广州牧使边应星等。赍持谷物。百计赈活。而缘无食物。所活终是不广。臣军官部将郭护赈救引出于江华者。男女老弱并九百馀名。李蘋军官羽林卫成男前后赈救者二百馀人。其他诸阵出来者。陆续不绝。而或多气尽僵仆道路而死者。马山驿近处。有一乳下之儿。其母已死。而在傍呱呱。天将查总兵见而哀之。令军丁马上抱来。在旁养饲。情甚悲痛。大抵京畿数百里内。无复馀蓄。民生如聚涸辙之鱼。计日待尽。欲救则无谷。不救则难忍。南方之谷。以天兵粮饷来到江口者。近日颇集。在东坡者有米豆万馀石。其在后西江者亦有数千馀石。此外唐粮。及时来到。则大军虽复回来。而势可支给。其中各官输转荒正租二千馀石。亦在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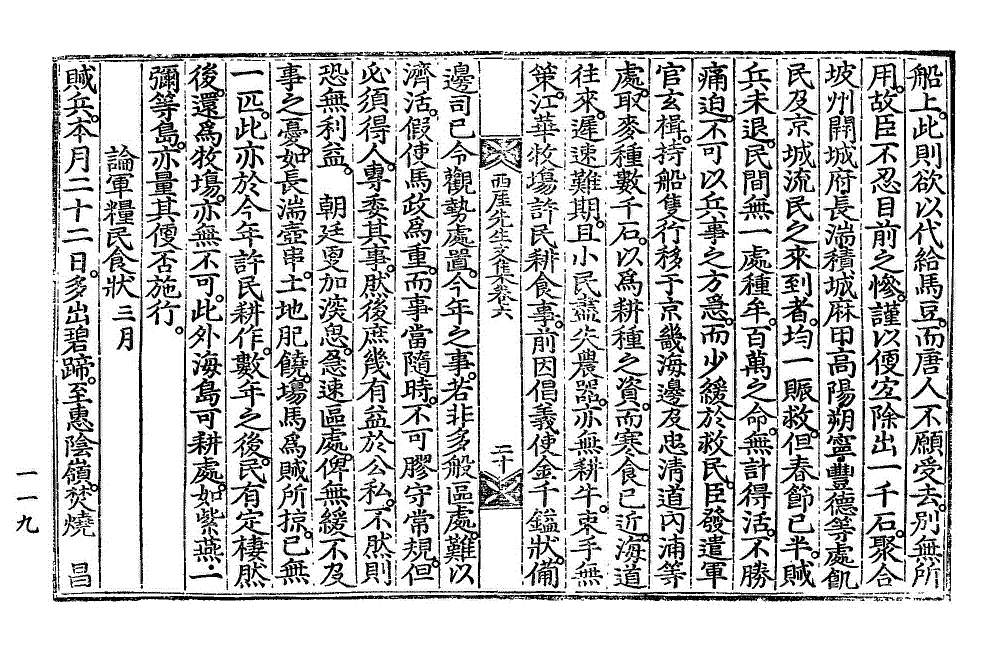 船上。此则欲以代给马豆。而唐人不愿受去。别无所用。故臣不忍目前之惨。谨以便宜除出一千石。聚合坡州,开城府,长湍,积城,麻田,高阳,朔宁,丰德等处饥民及京城流民之来到者。均一赈救。但春节已半。贼兵未退。民间无一处种牟。百万之命。无计得活。不胜痛迫。不可以兵事之方急。而少缓于救民。臣发遣军官玄楫。持船只行移于京畿海边及忠清道内浦等处。取麦种数千石。以为耕种之资。而寒食已近。海道往来。迟速难期。且小民尽失农器。亦无耕牛。束手无策。江华牧场许民耕食事。前因倡义使金千镒状。备边司已令观势处置。今年之事。若非多船区处。难以济活。假使马政为重。而事当随时。不可胶守常规。但必须得人。专委其事。然后庶几有益于公私。不然则恐无利益。 朝廷更加深思。急速区处。俾无缓不及事之忧。如长湍壶串。土地肥饶。场马为贼所掠。已无一匹。此亦于今年许民耕作。数年之后。民有定栖然后。还为牧场。亦无不可。此外海岛可耕处。如紫燕,一弥等岛。亦量其便否施行。
船上。此则欲以代给马豆。而唐人不愿受去。别无所用。故臣不忍目前之惨。谨以便宜除出一千石。聚合坡州,开城府,长湍,积城,麻田,高阳,朔宁,丰德等处饥民及京城流民之来到者。均一赈救。但春节已半。贼兵未退。民间无一处种牟。百万之命。无计得活。不胜痛迫。不可以兵事之方急。而少缓于救民。臣发遣军官玄楫。持船只行移于京畿海边及忠清道内浦等处。取麦种数千石。以为耕种之资。而寒食已近。海道往来。迟速难期。且小民尽失农器。亦无耕牛。束手无策。江华牧场许民耕食事。前因倡义使金千镒状。备边司已令观势处置。今年之事。若非多船区处。难以济活。假使马政为重。而事当随时。不可胶守常规。但必须得人。专委其事。然后庶几有益于公私。不然则恐无利益。 朝廷更加深思。急速区处。俾无缓不及事之忧。如长湍壶串。土地肥饶。场马为贼所掠。已无一匹。此亦于今年许民耕作。数年之后。民有定栖然后。还为牧场。亦无不可。此外海岛可耕处。如紫燕,一弥等岛。亦量其便否施行。论军粮民食状(三月)
贼兵。本月二十二日。多出碧蹄。至惠阴岭。焚烧 昌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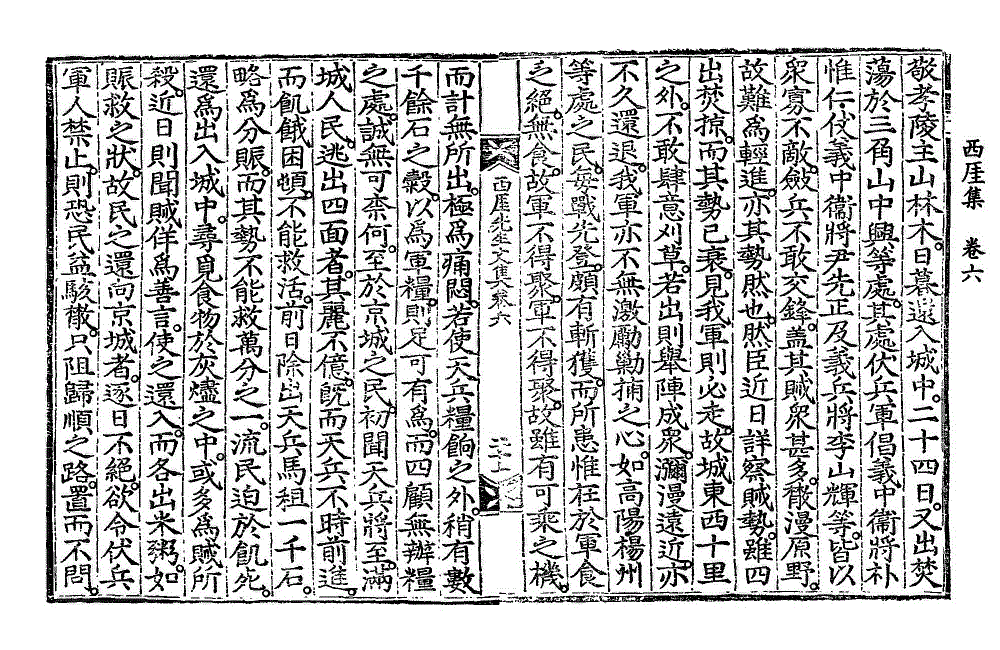 敬孝陵主山林木。日暮还入城中。二十四日。又出焚荡于三角山中兴等处。其处伏兵军倡义中卫将朴惟仁,仗义中卫将尹先正及义兵将李山辉等。皆以众寡不敌。敛兵不敢交锋。盖其贼众甚多。散漫原野。故难为轻进。亦其势然也。然臣近日详察贼势。虽四出焚掠。而其势已衰。见我军则必走。故城东西十里之外。不敢肆意刈草。若出则举阵成众。瀰漫远近。亦不久还退。我军亦不无激励剿捕之心。如高阳,杨州等处之民。每战先登。颇有斩获。而所患惟在于军食乏绝。无食。故军不得聚。军不得聚。故虽有可乘之机。而计无所出。极为痛闷。若使天兵粮饷之外。稍有数千馀石之谷。以为军粮。则足可有为。而四顾无办粮之处。诚无可柰何。至于京城之民。初闻天兵将至。满城人民。逃出四面者。其丽不亿。既而天兵不时前进。而饥饿困顿。不能救活。前日除出天兵马租一千石。略为分赈。而其势不能救万分之一。流民迫于饥死。还为出入城中。寻觅食物于灰烬之中。或多为贼所杀。近日则闻贼佯为善言。使之还入。而各出米粥。如赈救之状。故民之还向京城者。逐日不绝。欲令伏兵军人禁止。则恐民益骇散。只阻归顺之路。置而不问。
敬孝陵主山林木。日暮还入城中。二十四日。又出焚荡于三角山中兴等处。其处伏兵军倡义中卫将朴惟仁,仗义中卫将尹先正及义兵将李山辉等。皆以众寡不敌。敛兵不敢交锋。盖其贼众甚多。散漫原野。故难为轻进。亦其势然也。然臣近日详察贼势。虽四出焚掠。而其势已衰。见我军则必走。故城东西十里之外。不敢肆意刈草。若出则举阵成众。瀰漫远近。亦不久还退。我军亦不无激励剿捕之心。如高阳,杨州等处之民。每战先登。颇有斩获。而所患惟在于军食乏绝。无食。故军不得聚。军不得聚。故虽有可乘之机。而计无所出。极为痛闷。若使天兵粮饷之外。稍有数千馀石之谷。以为军粮。则足可有为。而四顾无办粮之处。诚无可柰何。至于京城之民。初闻天兵将至。满城人民。逃出四面者。其丽不亿。既而天兵不时前进。而饥饿困顿。不能救活。前日除出天兵马租一千石。略为分赈。而其势不能救万分之一。流民迫于饥死。还为出入城中。寻觅食物于灰烬之中。或多为贼所杀。近日则闻贼佯为善言。使之还入。而各出米粥。如赈救之状。故民之还向京城者。逐日不绝。欲令伏兵军人禁止。则恐民益骇散。只阻归顺之路。置而不问。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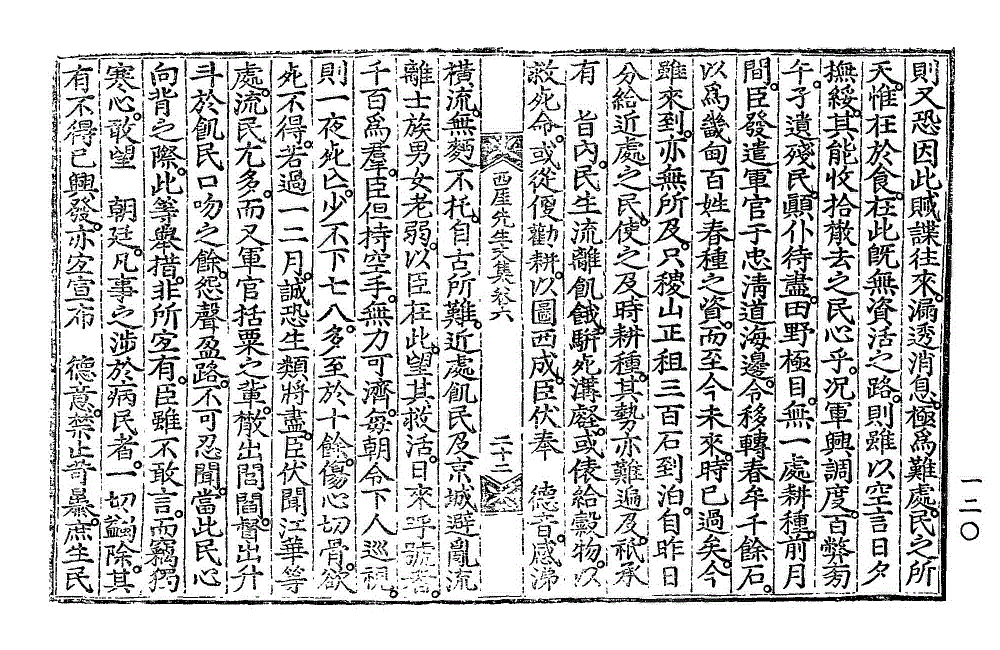 则又恐因此贼谍往来。漏透消息。极为难处。民之所天。惟在于食。在此既无资活之路。则虽以空言日夕抚绥。其能收拾散去之民心乎。况军兴调度。百弊旁午。孑遗残民。颠仆待尽。田野极目。无一处耕种。前月间。臣发遣军官于忠清道海边。令移转春牟千馀石。以为畿甸百姓春种之资。而至今未来。时已过矣。今虽来到。亦无所及。只稷山正租三百石到泊。自昨日分给近处之民。使之及时耕种。其势亦难遍及。祇承有 旨内。民生流离饥饿。骈死沟壑。或俵给谷物。以救死命。或从便劝耕。以图西成。臣伏奉 德音。感涕横流。无面不托。自古所难。近处饥民及京城避乱流离士族男女老弱。以臣在此。望其救活。日来呼号者。千百为群。臣但持空手。无力可济。每朝令下人巡视。则一夜死亡。少不下七八。多至于十馀。伤心切骨。欲死不得。若过一二月。诚恐生类将尽。臣伏闻江华等处。流民尤多。而又军官括粟之辈。散出闾阎。督出升斗于饥民口吻之馀。怨声盈路。不可忍闻。当此民心向背之际。此等举措。非所宜有。臣虽不敢言。而窃独寒心。敢望 朝廷。凡事之涉于病民者。一切蠲除。其有不得已兴发。亦宜宣布 德意。禁止苛暴。庶生民
则又恐因此贼谍往来。漏透消息。极为难处。民之所天。惟在于食。在此既无资活之路。则虽以空言日夕抚绥。其能收拾散去之民心乎。况军兴调度。百弊旁午。孑遗残民。颠仆待尽。田野极目。无一处耕种。前月间。臣发遣军官于忠清道海边。令移转春牟千馀石。以为畿甸百姓春种之资。而至今未来。时已过矣。今虽来到。亦无所及。只稷山正租三百石到泊。自昨日分给近处之民。使之及时耕种。其势亦难遍及。祇承有 旨内。民生流离饥饿。骈死沟壑。或俵给谷物。以救死命。或从便劝耕。以图西成。臣伏奉 德音。感涕横流。无面不托。自古所难。近处饥民及京城避乱流离士族男女老弱。以臣在此。望其救活。日来呼号者。千百为群。臣但持空手。无力可济。每朝令下人巡视。则一夜死亡。少不下七八。多至于十馀。伤心切骨。欲死不得。若过一二月。诚恐生类将尽。臣伏闻江华等处。流民尤多。而又军官括粟之辈。散出闾阎。督出升斗于饥民口吻之馀。怨声盈路。不可忍闻。当此民心向背之际。此等举措。非所宜有。臣虽不敢言。而窃独寒心。敢望 朝廷。凡事之涉于病民者。一切蠲除。其有不得已兴发。亦宜宣布 德意。禁止苛暴。庶生民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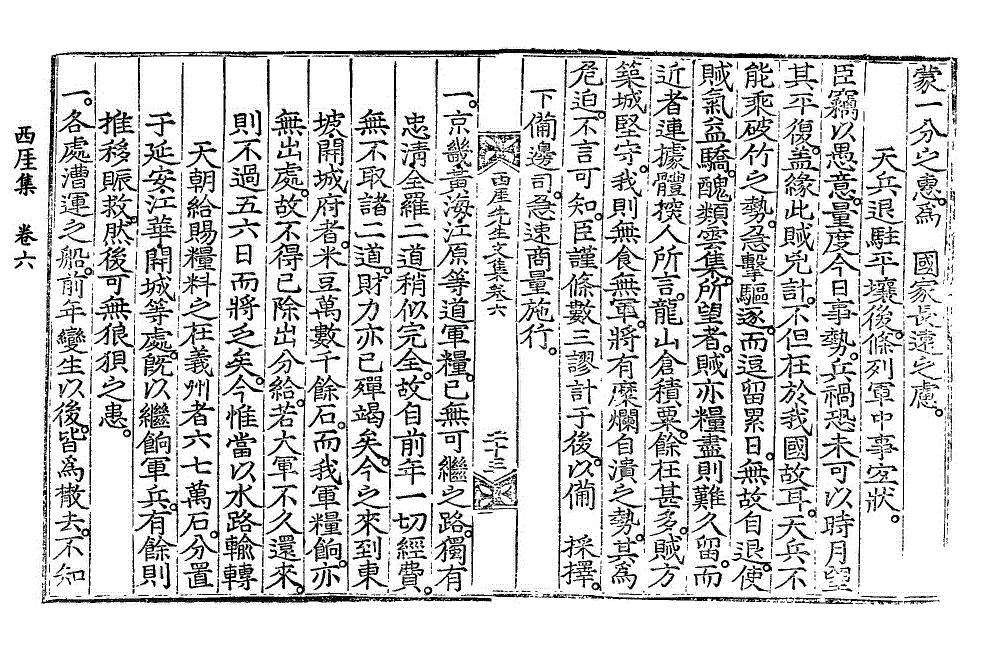 蒙一分之惠。为 国家长远之虑。
蒙一分之惠。为 国家长远之虑。天兵退驻平壤后。条列军中事宜状。
臣窃以愚意。量度今日事势。兵祸恐未可以时月望其平复。盖缘此贼凶计。不但在于我国故耳。天兵不能乘破竹之势。急击驱逐。而逗留累日。无故自退。使贼气益骄。丑类云集。所望者。贼亦粮尽则难久留。而近者连据体探人所言。龙山仓积粟。馀在甚多。贼方筑城坚守。我则无食无军。将有糜烂自溃之势。其为危迫。不言可知。臣谨条数三谬计于后。以备 采择。 下备边司。急速商量施行。
一。京畿,黄海,江原等道军粮。已无可继之路。独有忠清,全罗二道稍似完全。故自前年一切经费。无不取诸二道。财力亦已殚竭矣。今之来到东坡,开城府者。米豆万数千馀石。而我军粮饷。亦无出处。故不得已除出分给。若大军不久还来。则不过五六日而将乏矣。今惟当以水路输转 天朝给赐粮料之在义州者六七万石。分置于延安,江华,开城等处。既以继饷军兵。有馀则推移赈救。然后可无狼狈之患。
一。各处漕运之船。前年变生以后。皆为散去。不知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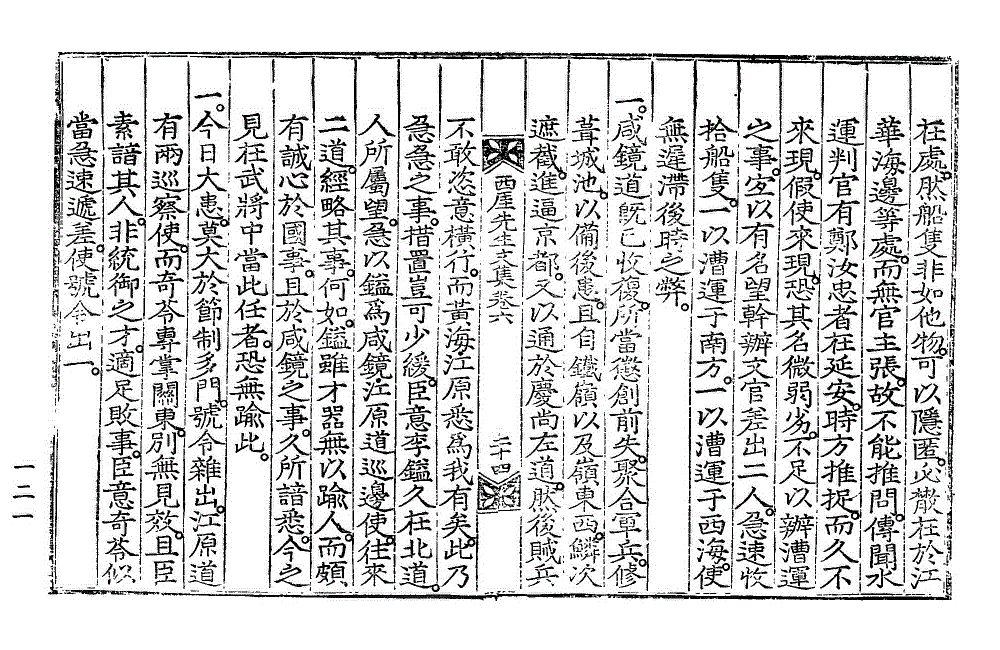 在处。然船集非如他物。可以隐匿。必散在于江华海边等处。而无官主张。故不能推问。传闻水运判官有郑汝忠者在延安。时方推捉。而久不来现。假使来现。恐其名微弱劣。不足以办漕运之事。宜以有名望干办文官差出二人。急速收拾船只。一以漕运于南方。一以漕运于西海。使无迟滞后时之弊。
在处。然船集非如他物。可以隐匿。必散在于江华海边等处。而无官主张。故不能推问。传闻水运判官有郑汝忠者在延安。时方推捉。而久不来现。假使来现。恐其名微弱劣。不足以办漕运之事。宜以有名望干办文官差出二人。急速收拾船只。一以漕运于南方。一以漕运于西海。使无迟滞后时之弊。一。咸镜道既已收复。所当惩创前失。聚合军兵。修葺城池。以备后患。且自铁岭以及岭东西。鳞次遮截。进逼京都。又以通于庆尚左道。然后贼兵不敢恣意横行。而黄海,江原悉为我有矣。此乃急急之事。措置岂可少缓。臣意李镒久在北道。人所属望。急以镒为咸镜,江原道巡边使。往来二道。经略其事。何如。镒虽才器无以踰人。而颇有诚心于国事。且于咸镜之事。久所谙悉。今之见在武将中当此任者。恐无踰此。
一。今日大患。莫大于节制多门。号令杂出。江原道有两巡察使。而奇苓专掌关东。别无见效。且臣素谙其人。非统御之才。适足败事。臣意奇苓似当急速递差。使号令出一。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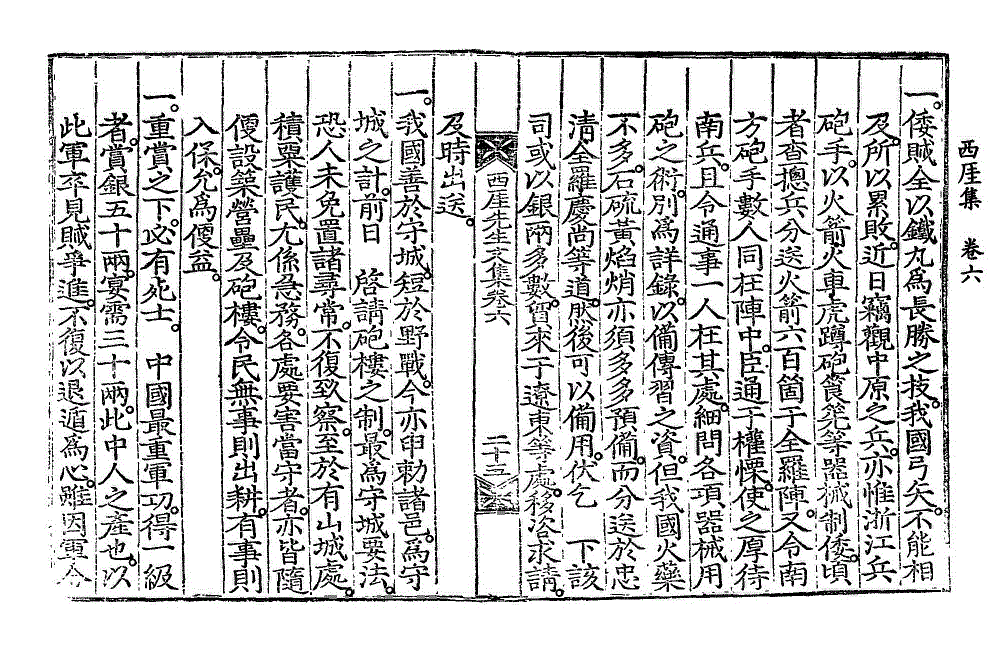 一。倭贼全以铁丸为长胜之技。我国弓矢。不能相及。所以累败。近日窃观中原之兵。亦惟浙江兵炮手。以火箭,火车,虎蹲炮,筤筅等器械制倭。顷者查总兵分送火箭六百个于全罗阵。又令南方炮手数人同在阵中。臣通于权慄。使之厚待南兵。且令通事一人在其处。细问各项器械用炮之术。别为详录。以备传习之资。但我国火药不多。石硫黄焰焇亦须多多预备。而分送于忠清,全罗,庆尚等道。然后可以备用。伏乞 下该司或以银两多数。贸来于辽东等处。移咨求请。及时出送。
一。倭贼全以铁丸为长胜之技。我国弓矢。不能相及。所以累败。近日窃观中原之兵。亦惟浙江兵炮手。以火箭,火车,虎蹲炮,筤筅等器械制倭。顷者查总兵分送火箭六百个于全罗阵。又令南方炮手数人同在阵中。臣通于权慄。使之厚待南兵。且令通事一人在其处。细问各项器械用炮之术。别为详录。以备传习之资。但我国火药不多。石硫黄焰焇亦须多多预备。而分送于忠清,全罗,庆尚等道。然后可以备用。伏乞 下该司或以银两多数。贸来于辽东等处。移咨求请。及时出送。一。我国善于守城。短于野战。今亦申敕诸邑。为守城之计。前日 启请炮楼之制。最为守城要法。恐人未免置诸寻常。不复致察。至于有山城处。积粟护民。尤系急务。各处要害当守者。亦皆随便设筑营垒及炮楼。令民无事则出耕。有事则入保。允为便益。
一。重赏之下。必有死士。 中国最重军功。得一级者。赏银五十两。宴需三十两。此中人之产也。以此军卒见贼争进。不复以退遁为心。虽因军令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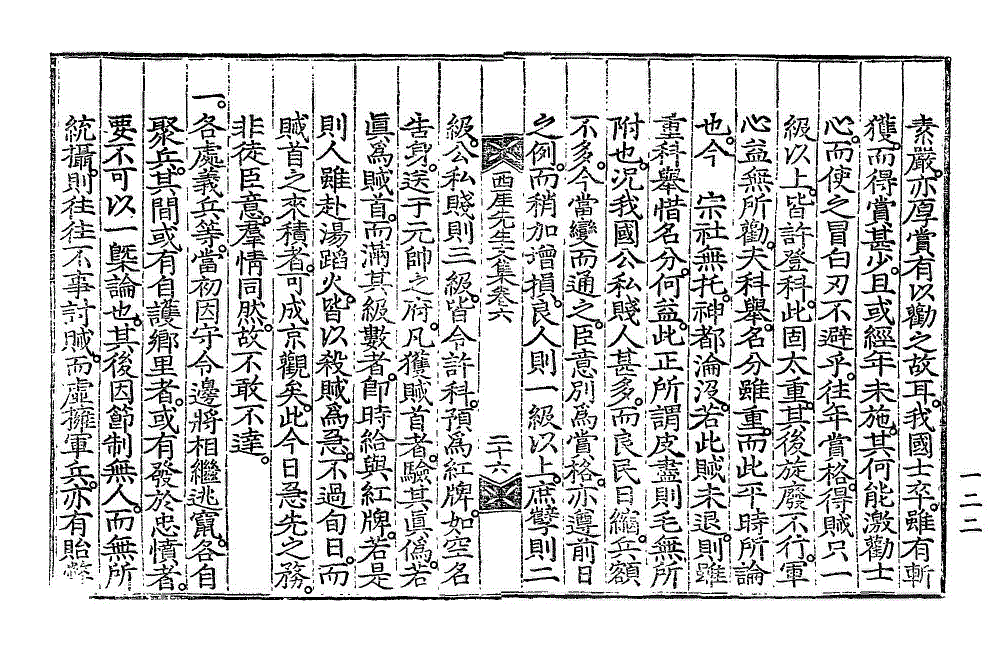 素严。亦厚赏有以劝之故耳。我国士卒。虽有斩获。而得赏甚少。且或经年未施。其何能激劝士心。而使之冒白刃不避乎。往年赏格。得贼只一级以上。皆许登科。此固太重。其后旋废不行。军心益无所劝。夫科举。名分虽重。而此平时所论也。今 宗社无托。神都沦没。若此贼未退。则虽重科举惜名分。何益。此正所谓皮尽则毛无所附也。况我国公私贱人甚多。而良民日缩。兵额不多。今当变而通之。臣意别为赏格。亦遵前日之例。而稍加增损。良人则一级以上。庶孽则二级。公私贱则三级。皆令许科。预为红牌。如空名告身。送于元帅之府。凡获贼首者。验其真伪。若真为贼首。而满其级数者。即时给与红牌。若是则人虽赴汤蹈火。皆以杀贼为急。不过旬日。而贼首之来积者。可成京观矣。此今日急先之务。非徒臣意。群情同然。故不敢不达。
素严。亦厚赏有以劝之故耳。我国士卒。虽有斩获。而得赏甚少。且或经年未施。其何能激劝士心。而使之冒白刃不避乎。往年赏格。得贼只一级以上。皆许登科。此固太重。其后旋废不行。军心益无所劝。夫科举。名分虽重。而此平时所论也。今 宗社无托。神都沦没。若此贼未退。则虽重科举惜名分。何益。此正所谓皮尽则毛无所附也。况我国公私贱人甚多。而良民日缩。兵额不多。今当变而通之。臣意别为赏格。亦遵前日之例。而稍加增损。良人则一级以上。庶孽则二级。公私贱则三级。皆令许科。预为红牌。如空名告身。送于元帅之府。凡获贼首者。验其真伪。若真为贼首。而满其级数者。即时给与红牌。若是则人虽赴汤蹈火。皆以杀贼为急。不过旬日。而贼首之来积者。可成京观矣。此今日急先之务。非徒臣意。群情同然。故不敢不达。一。各处义兵等。当初因守令边将相继逃窜。各自聚兵。其间或有自护乡里者。或有发于忠愤者。要不可以一槩论也。其后因节制无人。而无所统摄。则往往不事讨贼。而虚拥军兵。亦有贻弊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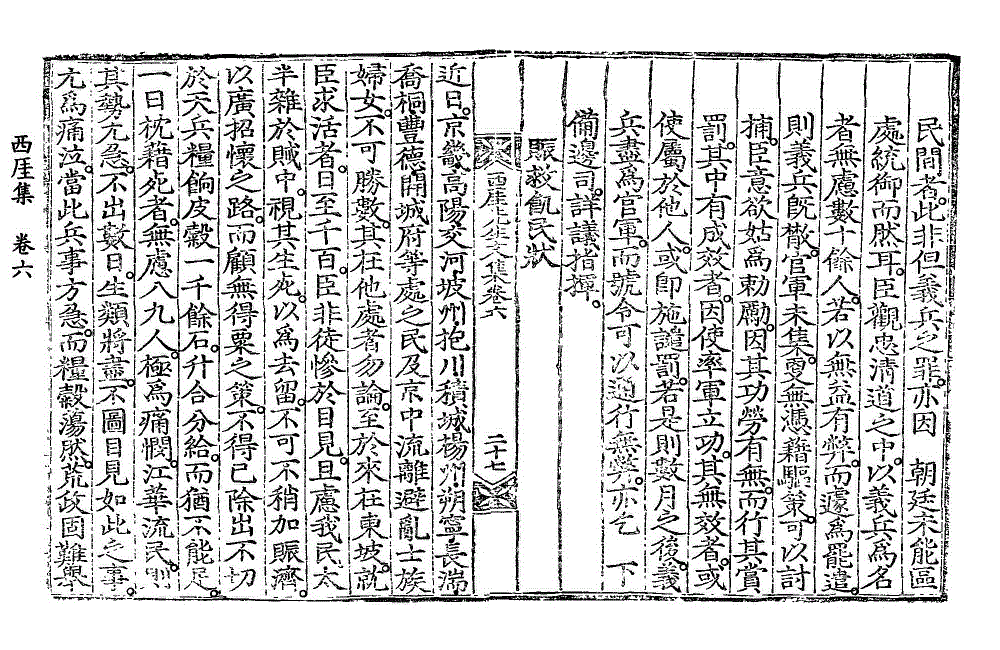 民间者。此非但义兵之罪。亦因 朝廷未能区处统御而然耳。臣观忠清道之中。以义兵为名者无虑数十馀人。若以无益有弊。而遽为罢遣。则义兵既散。官军未集。更无凭藉驱策。可以讨捕。臣意欲姑为敕励。因其功劳有无。而行其赏罚。其中有成效者。因使率军立功。其无效者。或使属于他人。或即施谴罚。若是则数月之后。义兵尽为官军。而号令可以通行无弊。亦乞 下备边司。详议指挥。
民间者。此非但义兵之罪。亦因 朝廷未能区处统御而然耳。臣观忠清道之中。以义兵为名者无虑数十馀人。若以无益有弊。而遽为罢遣。则义兵既散。官军未集。更无凭藉驱策。可以讨捕。臣意欲姑为敕励。因其功劳有无。而行其赏罚。其中有成效者。因使率军立功。其无效者。或使属于他人。或即施谴罚。若是则数月之后。义兵尽为官军。而号令可以通行无弊。亦乞 下备边司。详议指挥。赈救饥民状
近日。京畿,高阳,交河,坡州,抱川,积城,杨州,朔宁,长湍,乔桐,丰德,开城府等处之民及京中流离避乱士族妇女。不可胜数。其在他处者勿论。至于来在东坡。就臣求活者。日至千百。臣非徒惨于目见。且虑我民太半杂于贼中。视其生死。以为去留。不可不稍加赈济。以广招怀之路。而顾无得粟之策。不得已除出不切于天兵粮饷皮谷一千馀石。升合分给。而犹不能足。一日枕藉死者。无虑八九人。极为痛悯。江华流民。则其势尤急。不出数日。生类将尽。不图目见如此之事。尤为痛泣。当此兵事方急。而粮谷荡然。荒政固难举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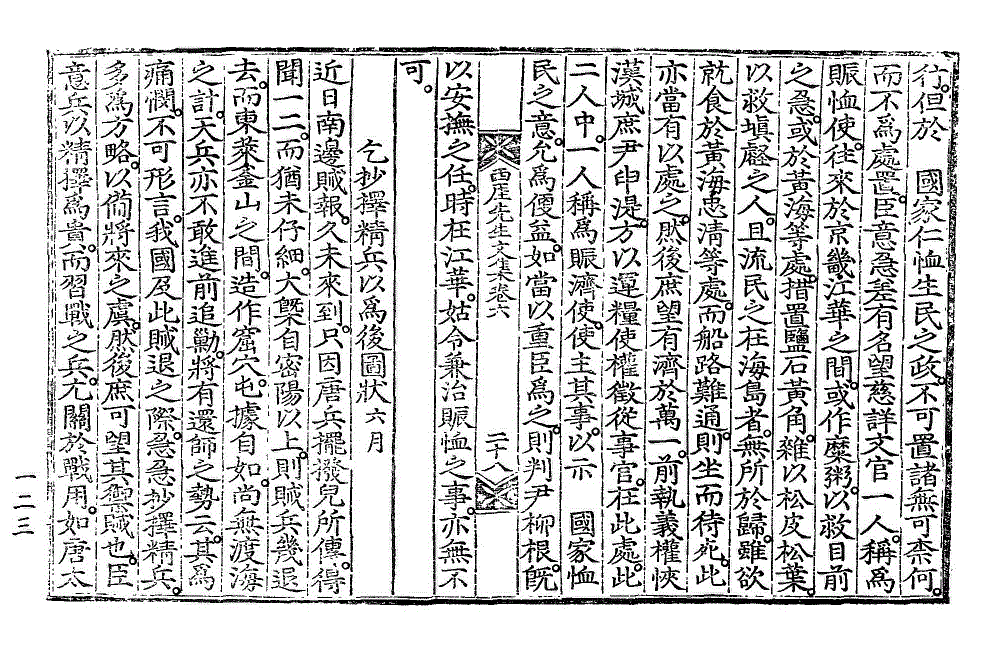 行。但于 国家仁恤生民之政。不可置诸无可柰何。而不为处置。臣意急差有名望慈详文官一人。称为赈恤使。往来于京畿,江华之间。或作糜粥。以救目前之急。或于黄海等处。措置盐石黄角。杂以松皮松叶。以救填壑之人。且流民之在海岛者。无所于归。虽欲就食于黄海,忠清等处。而船路难通。则坐而待死。此亦当有以处之。然后庶望有济于万一。前执义权悏汉城庶尹申湜。方以运粮使权徵从事官。在此处。此二人中。一人称为赈济使。使主其事。以示 国家恤民之意。允为便益。如当以重臣为之。则判尹柳根。既以安抚之任。时在江华。姑令兼治赈恤之事。亦无不可。
行。但于 国家仁恤生民之政。不可置诸无可柰何。而不为处置。臣意急差有名望慈详文官一人。称为赈恤使。往来于京畿,江华之间。或作糜粥。以救目前之急。或于黄海等处。措置盐石黄角。杂以松皮松叶。以救填壑之人。且流民之在海岛者。无所于归。虽欲就食于黄海,忠清等处。而船路难通。则坐而待死。此亦当有以处之。然后庶望有济于万一。前执义权悏汉城庶尹申湜。方以运粮使权徵从事官。在此处。此二人中。一人称为赈济使。使主其事。以示 国家恤民之意。允为便益。如当以重臣为之。则判尹柳根。既以安抚之任。时在江华。姑令兼治赈恤之事。亦无不可。乞抄择精兵以为后图状(六月)
近日南边贼报。久未来到。只因唐兵摆拨儿所传。得闻一二。而犹未仔细。大槩自密阳以上。则贼兵几退去。而东莱,釜山之间。造作窟穴。屯据自如。尚无渡海之计。天兵亦不敢进前追剿。将有还师之势云。其为痛悯。不可形言。我国及此贼退之际。急急抄择精兵。多为方略。以备将来之虞。然后庶可望其御贼也。臣意兵以精择为贵。而习战之兵。尤关于战用。如唐太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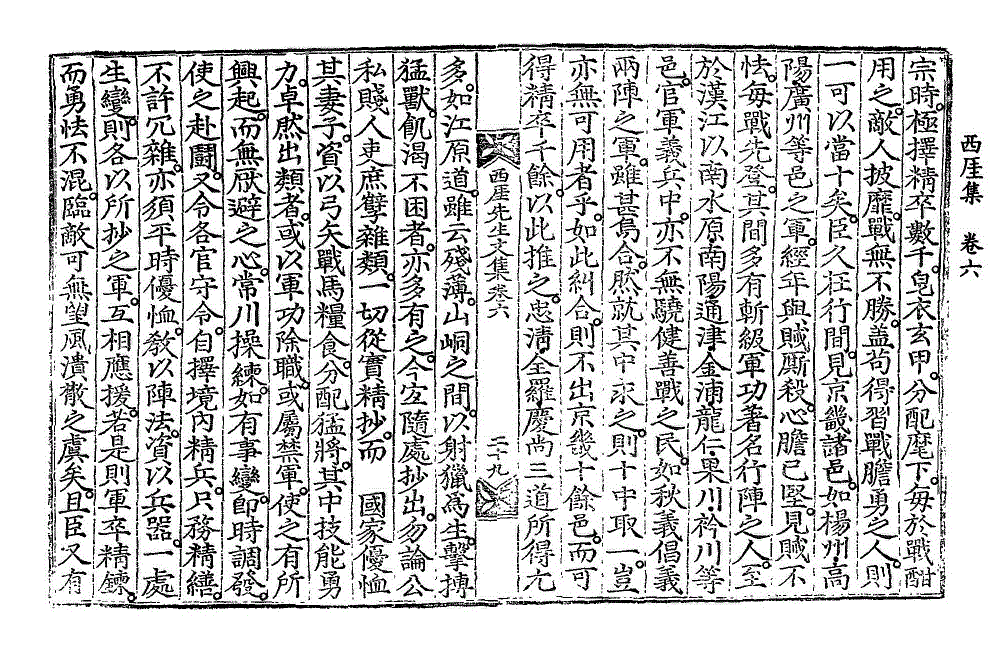 宗时。极择精卒数千。皂衣玄甲。分配麾下。每于战酣用之。敌人披靡。战无不胜。盖苟得习战胆勇之人。则一可以当十矣。臣久在行间。见京畿诸邑。如杨州,高阳,广州等邑之军。经年与贼厮杀。心胆已坚。见贼不怯。每战先登。其间多有斩级军功著名行阵之人。至于汉江以南水原,南阳,通津,金浦,龙仁,果川,衿川等邑。官军义兵中。亦不无骁健善战之民。如秋义倡义两阵之军。虽甚乌合。然就其中求之。则十中取一。岂亦无可用者乎。如此纠合。则不出京畿十馀邑。而可得精卒千馀。以此推之。忠清,全罗,庆尚三道所得尤多。如江原道。虽云残薄。山峒之间。以射猎为生。击搏猛兽。饥渴不困者。亦多有之。今宜随处抄出。勿论公私贱人吏庶孽杂类。一切从实精抄。而 国家优恤其妻子。资以弓矢战马粮食。分配猛将。其中技能勇力。卓然出类者。或以军功除职。或属禁军。使之有所兴起。而无厌避之心。常川操练。如有事变。即时调发。使之赴斗。又令各官守令。自择境内精兵。只务精缮。不许冗杂。亦须平时优恤。教以阵法。资以兵器。一处生变。则各以所抄之军。互相应援。若是则军卒精鍊。而勇怯不混。临敌可无望风溃散之虞矣。且臣又有
宗时。极择精卒数千。皂衣玄甲。分配麾下。每于战酣用之。敌人披靡。战无不胜。盖苟得习战胆勇之人。则一可以当十矣。臣久在行间。见京畿诸邑。如杨州,高阳,广州等邑之军。经年与贼厮杀。心胆已坚。见贼不怯。每战先登。其间多有斩级军功著名行阵之人。至于汉江以南水原,南阳,通津,金浦,龙仁,果川,衿川等邑。官军义兵中。亦不无骁健善战之民。如秋义倡义两阵之军。虽甚乌合。然就其中求之。则十中取一。岂亦无可用者乎。如此纠合。则不出京畿十馀邑。而可得精卒千馀。以此推之。忠清,全罗,庆尚三道所得尤多。如江原道。虽云残薄。山峒之间。以射猎为生。击搏猛兽。饥渴不困者。亦多有之。今宜随处抄出。勿论公私贱人吏庶孽杂类。一切从实精抄。而 国家优恤其妻子。资以弓矢战马粮食。分配猛将。其中技能勇力。卓然出类者。或以军功除职。或属禁军。使之有所兴起。而无厌避之心。常川操练。如有事变。即时调发。使之赴斗。又令各官守令。自择境内精兵。只务精缮。不许冗杂。亦须平时优恤。教以阵法。资以兵器。一处生变。则各以所抄之军。互相应援。若是则军卒精鍊。而勇怯不混。临敌可无望风溃散之虞矣。且臣又有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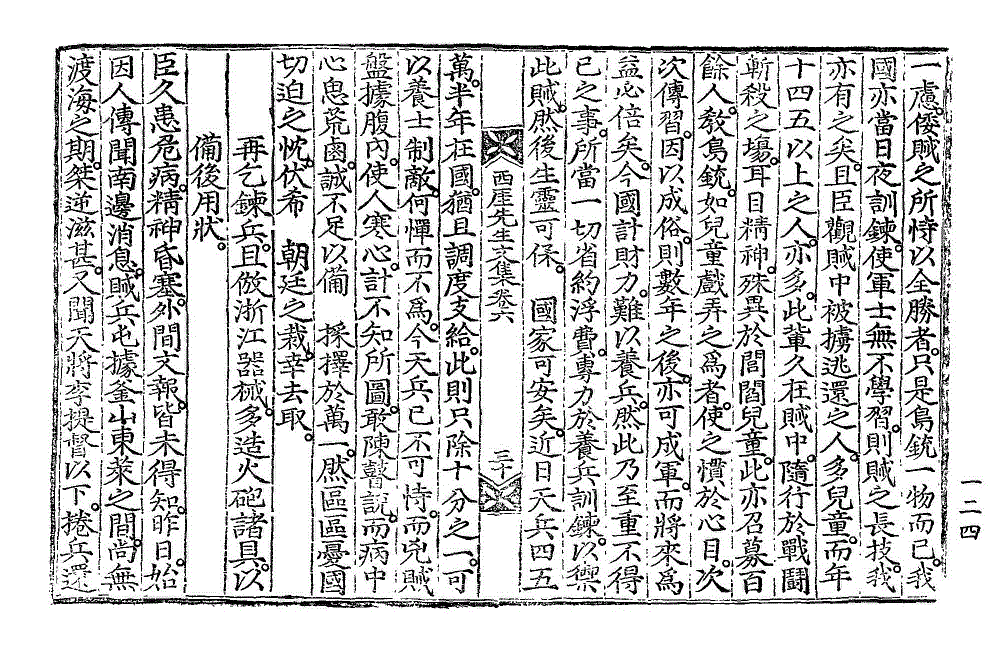 一虑。倭贼之所恃以全胜者。只是鸟铳一物而已。我国亦当日夜训鍊。使军士无不学习。则贼之长技。我亦有之矣。且臣观贼中被掳逃还之人。多儿童。而年十四五以上之人。亦多。此辈久在贼中。随行于战斗斩杀之场。耳目精神。殊异于闾阎儿童。此亦召募百馀人。教鸟铳。如儿童戏弄之为者。使之惯于心目。次次传习。因以成俗。则数年之后。亦可成军。而将来为益必倍矣。今国计财力。难以养兵。然此乃至重不得已之事。所当一切省约浮费。专力于养兵训鍊。以御此贼。然后生灵可保。 国家可安矣。近日天兵四五万。半年在国。犹且调度支给。此则只除十分之一。可以养士制敌。何惮而不为。今天兵已不可恃。而凶贼盘据腹内。使人寒心。计不知所图。敢陈瞽说。而病中心思荒卤。诚不足以备 采择于万一。然区区忧国切迫之忱。伏希 朝廷之裁。幸去取。
一虑。倭贼之所恃以全胜者。只是鸟铳一物而已。我国亦当日夜训鍊。使军士无不学习。则贼之长技。我亦有之矣。且臣观贼中被掳逃还之人。多儿童。而年十四五以上之人。亦多。此辈久在贼中。随行于战斗斩杀之场。耳目精神。殊异于闾阎儿童。此亦召募百馀人。教鸟铳。如儿童戏弄之为者。使之惯于心目。次次传习。因以成俗。则数年之后。亦可成军。而将来为益必倍矣。今国计财力。难以养兵。然此乃至重不得已之事。所当一切省约浮费。专力于养兵训鍊。以御此贼。然后生灵可保。 国家可安矣。近日天兵四五万。半年在国。犹且调度支给。此则只除十分之一。可以养士制敌。何惮而不为。今天兵已不可恃。而凶贼盘据腹内。使人寒心。计不知所图。敢陈瞽说。而病中心思荒卤。诚不足以备 采择于万一。然区区忧国切迫之忱。伏希 朝廷之裁。幸去取。再乞鍊兵。且仿浙江器械。多造火炮诸具。以备后用状。
臣久患危病。精神昏塞。外间文报。皆未得知。昨日。始因人传闻南边消息。贼兵屯据釜山,东莱之间。尚无渡海之期。桀逆滋甚。又闻天将李提督以下。捲兵还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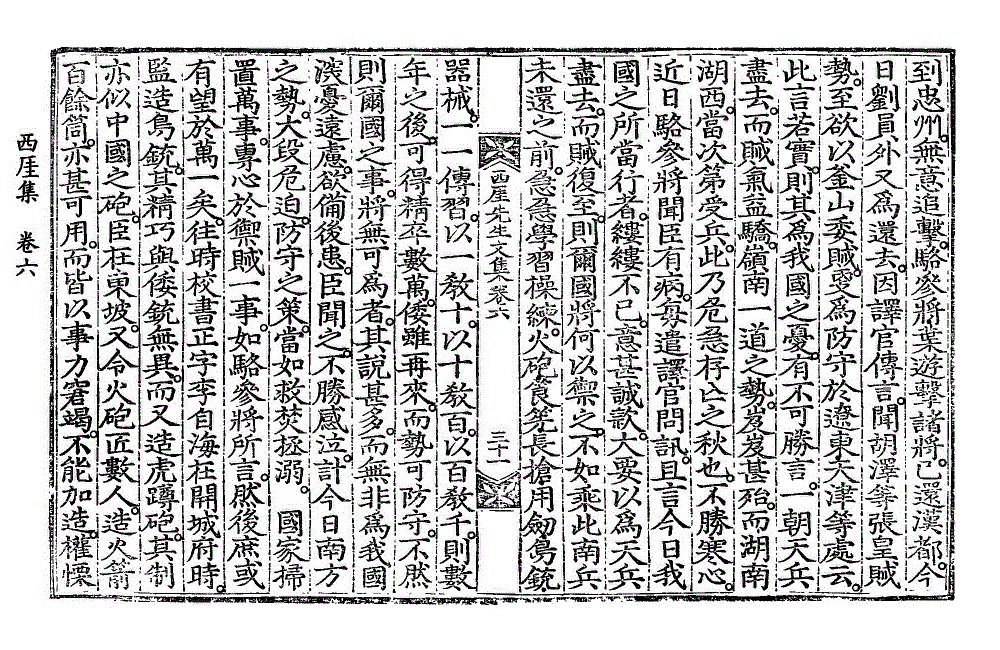 到忠州。无意追击。骆参将,叶游击诸将。已还汉都。今日刘员外又为还去。因译官传言。闻胡泽等张皇贼势。至欲以釜山委贼。更为防守于辽东,天津等处云。此言若实。则其为我国之忧。有不可胜言。一朝天兵尽去。而贼气益骄。岭南一道之势。岌岌甚殆。而湖南湖西。当次第受兵。此乃危急存亡之秋也。不胜寒心。近日骆参将闻臣有病。每遣译官问讯。且言今日我国之所当行者。缕缕不已。意甚诚款。大要以为天兵尽去。而贼复至。则尔国将何以御之。不如乘此南兵未还之前。急急学习操练。火炮,筤筅,长抢,用剑,鸟铳,器械。一一传习。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则数年之后。可得精卒数万。倭虽再来。而势可防守。不然则尔国之事。将无可为者。其说甚多。而无非为我国深忧远虑。欲备后患。臣闻之。不胜感泣。计今日南方之势。大段危迫。防守之策。当如救焚拯溺。 国家扫置万事。专心于御贼一事。如骆参将所言。然后庶或有望于万一矣。往时校书正字李自海在开城府时。监造鸟铳。其精巧与倭铳无异。而又造虎蹲炮。其制亦似中国之炮。臣在东坡。又令火炮匠数人。造火箭百馀筒。亦甚可用。而皆以事力窘竭。不能加造。权慄
到忠州。无意追击。骆参将,叶游击诸将。已还汉都。今日刘员外又为还去。因译官传言。闻胡泽等张皇贼势。至欲以釜山委贼。更为防守于辽东,天津等处云。此言若实。则其为我国之忧。有不可胜言。一朝天兵尽去。而贼气益骄。岭南一道之势。岌岌甚殆。而湖南湖西。当次第受兵。此乃危急存亡之秋也。不胜寒心。近日骆参将闻臣有病。每遣译官问讯。且言今日我国之所当行者。缕缕不已。意甚诚款。大要以为天兵尽去。而贼复至。则尔国将何以御之。不如乘此南兵未还之前。急急学习操练。火炮,筤筅,长抢,用剑,鸟铳,器械。一一传习。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则数年之后。可得精卒数万。倭虽再来。而势可防守。不然则尔国之事。将无可为者。其说甚多。而无非为我国深忧远虑。欲备后患。臣闻之。不胜感泣。计今日南方之势。大段危迫。防守之策。当如救焚拯溺。 国家扫置万事。专心于御贼一事。如骆参将所言。然后庶或有望于万一矣。往时校书正字李自海在开城府时。监造鸟铳。其精巧与倭铳无异。而又造虎蹲炮。其制亦似中国之炮。臣在东坡。又令火炮匠数人。造火箭百馀筒。亦甚可用。而皆以事力窘竭。不能加造。权慄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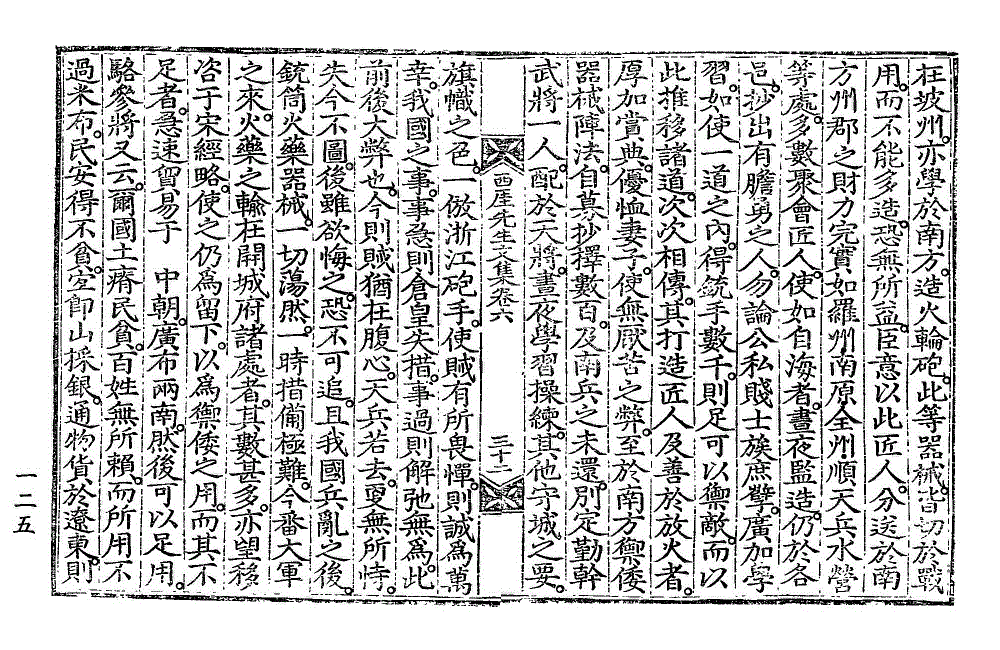 在坡州。亦学于南方。造火轮炮。此等器械。皆切于战用。而不能多造。恐无所益。臣意以此匠人。分送于南方州郡之财力完实如罗州,南原,全州,顺天兵水营等处。多数聚会匠人。使如自海者。昼夜监造。仍于各邑。抄出有胆勇之人。勿论公私贱士族庶孽。广加学习。如使一道之内。得铳手数千。则足可以御敌。而以此推移诸道。次次相传。其打造匠人及善于放火者。厚加赏典。优恤妻子。使无厌苦之弊。至于南方御倭器械阵法。自募抄择数百。及南兵之未还。别定勤干武将一人。配于天将。昼夜学习操练。其他守城之要。旗帜之色。一仿浙江炮手。使贼有所畏惮。则诚为万幸。我国之事。事急则仓皇失措。事过则解弛无为。此前后大弊也。今则贼犹在腹心。天兵若去。更无所恃。失今不图。后虽欲悔之。恐不可追。且我国兵乱之后。铳筒火药器械。一切荡然。一时措备极难。今番大军之来。火药之输在开城府诸处者。其数甚多。亦望移咨于宋经略。使之仍为留下。以为御倭之用。而其不足者。急速贸易于 中朝。广布两南。然后可以足用。骆参将又云。尔国土瘠民贫。百姓无所赖。而所用不过米布。民安得不贫。宜即山采银。通物货于辽东。则
在坡州。亦学于南方。造火轮炮。此等器械。皆切于战用。而不能多造。恐无所益。臣意以此匠人。分送于南方州郡之财力完实如罗州,南原,全州,顺天兵水营等处。多数聚会匠人。使如自海者。昼夜监造。仍于各邑。抄出有胆勇之人。勿论公私贱士族庶孽。广加学习。如使一道之内。得铳手数千。则足可以御敌。而以此推移诸道。次次相传。其打造匠人及善于放火者。厚加赏典。优恤妻子。使无厌苦之弊。至于南方御倭器械阵法。自募抄择数百。及南兵之未还。别定勤干武将一人。配于天将。昼夜学习操练。其他守城之要。旗帜之色。一仿浙江炮手。使贼有所畏惮。则诚为万幸。我国之事。事急则仓皇失措。事过则解弛无为。此前后大弊也。今则贼犹在腹心。天兵若去。更无所恃。失今不图。后虽欲悔之。恐不可追。且我国兵乱之后。铳筒火药器械。一切荡然。一时措备极难。今番大军之来。火药之输在开城府诸处者。其数甚多。亦望移咨于宋经略。使之仍为留下。以为御倭之用。而其不足者。急速贸易于 中朝。广布两南。然后可以足用。骆参将又云。尔国土瘠民贫。百姓无所赖。而所用不过米布。民安得不贫。宜即山采银。通物货于辽东。则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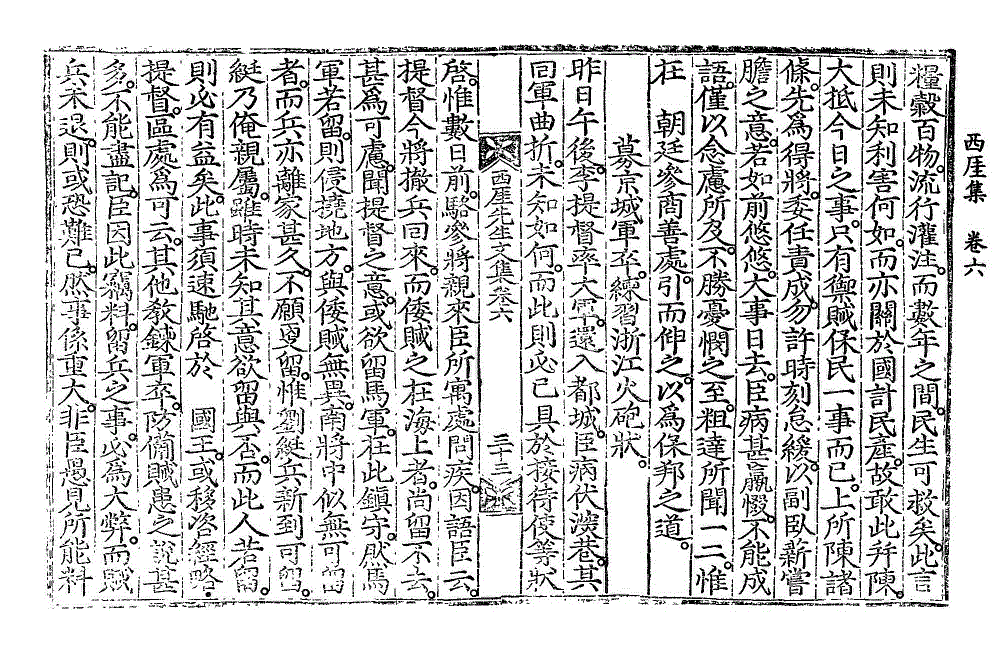 粮谷百物。流行灌注。而数年之间。民生可救矣。此言则未知利害何如。而亦关于国计民产。故敢此并陈。大抵今日之事。只有御贼保民一事而已。上所陈诸条。先为得将。委任责成。勿许时刻怠缓。以副卧薪尝胆之意。若如前悠悠。大事日去。臣病甚羸惙。不能成语。仅以念虑所及。不胜忧悯之至。粗达所闻一二。惟在 朝廷参商善处。引而伸之。以为保邦之道。
粮谷百物。流行灌注。而数年之间。民生可救矣。此言则未知利害何如。而亦关于国计民产。故敢此并陈。大抵今日之事。只有御贼保民一事而已。上所陈诸条。先为得将。委任责成。勿许时刻怠缓。以副卧薪尝胆之意。若如前悠悠。大事日去。臣病甚羸惙。不能成语。仅以念虑所及。不胜忧悯之至。粗达所闻一二。惟在 朝廷参商善处。引而伸之。以为保邦之道。募京城军卒。练习浙江火炮状。
昨日午后。李提督率大军。还入都城。臣病伏深巷。其回军曲折。未知如何。而此则必已具于接待使等状启。惟数日前。骆参将亲来臣所寓处问疾。因语臣云。提督今将撤兵回来。而倭贼之在海上者。尚留不去。甚为可虑。闻提督之意。或欲留马军。在此镇守。然马军若留。则侵挠地方。与倭贼无异。南将中似无可留者。而兵亦离家甚久。不愿更留。惟刘綎兵新到可留。綎乃俺亲属。虽时未知其意欲留与否。而此人若留。则必有益矣。此事须速驰启于 国王。或移咨经略,提督。区处为可云。其他教鍊军卒。防备贼患之说甚多。不能尽记。臣因此窃料。留兵之事。必为大弊。而贼兵未退。则或恐难已。然事系重大。非臣愚见所能料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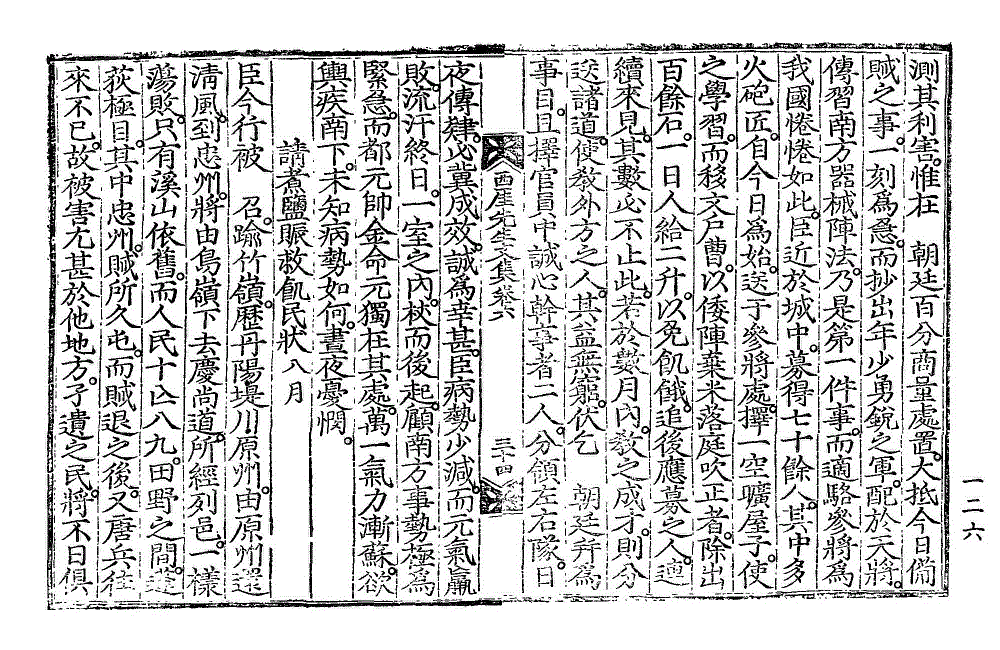 测其利害。惟在 朝廷百分商量处置。大抵今日备贼之事。一刻为急。而抄出年少勇锐之军。配于天将。传习南方器械阵法。乃是第一件事。而适骆参将为我国惓惓如此。臣近于城中。募得七十馀人。其中多火炮匠。自今日为始。送于参将处。择一空旷屋子。使之学习。而移文户曹。以倭阵弃米落庭吹正者。除出百馀石。一日人给二升。以免饥饿。追后应募之人。连续来见。其数必不止此。若于数月内。教之成才。则分送诸道。使教外方之人。其益无穷。伏乞 朝廷并为事目。且择官员中诚心干事者二人。分领左右队。日夜传肄。必冀成效。诚为幸甚。臣病势少减。而元气羸败。流汗终日。一室之内。杖而后起。顾南方事势极为紧急。而都元帅金命元独在其处。万一气力渐苏。欲舆疾南下。未知病势如何。昼夜忧悯。
测其利害。惟在 朝廷百分商量处置。大抵今日备贼之事。一刻为急。而抄出年少勇锐之军。配于天将。传习南方器械阵法。乃是第一件事。而适骆参将为我国惓惓如此。臣近于城中。募得七十馀人。其中多火炮匠。自今日为始。送于参将处。择一空旷屋子。使之学习。而移文户曹。以倭阵弃米落庭吹正者。除出百馀石。一日人给二升。以免饥饿。追后应募之人。连续来见。其数必不止此。若于数月内。教之成才。则分送诸道。使教外方之人。其益无穷。伏乞 朝廷并为事目。且择官员中诚心干事者二人。分领左右队。日夜传肄。必冀成效。诚为幸甚。臣病势少减。而元气羸败。流汗终日。一室之内。杖而后起。顾南方事势极为紧急。而都元帅金命元独在其处。万一气力渐苏。欲舆疾南下。未知病势如何。昼夜忧悯。请煮盐赈救饥民状(八月)
臣今行被 召。踰竹岭。历丹阳,堤川,原州。由原州还清风。到忠州。将由鸟岭下去庆尚道。所经列色。一样荡败。只有溪山依旧。而人民十亡八九。田野之间。蓬荻极目。其中忠州。贼所久屯。而贼退之后。又唐兵往来不已。故被害尤甚于他地方。孑遗之民。将不日俱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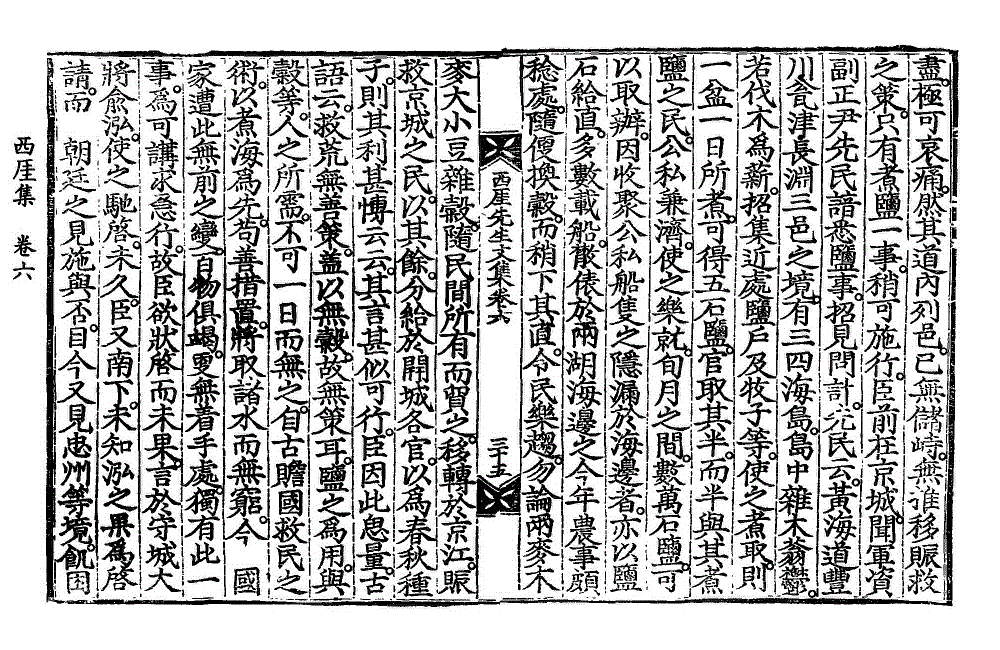 尽。极可哀痛。然其道内列色。已无储峙。无推移赈救之策。只有煮盐一事。稍可施行。臣前在京城。闻军资副正尹先民谙悉盐事。招见问计。先民云。黄海道丰川,瓮津,长渊三邑之境。有三四海岛。岛中杂木蓊郁。若伐木为薪。招集近处盐户及牧子等。使之煮取。则一盆一日所煮。可得五石盐。官取其半。而半与其煮盐之民。公私兼济。使之乐就。旬月之间。数万石盐。可以取办。因收聚公私船只之隐漏于海边者。亦以盐石给直。多数载船。散俵于两湖海边之今年农事颇稔处。随便换谷。而稍下其直。令民乐趋。勿论两麦木麦大小豆杂谷。随民间所有而贸之。移转于京江。赈救京城之民。以其馀。分给于开城各官。以为春秋种子。则其利甚博云云。其言甚似可行。臣因此思量。古语云。救荒无善策。盖以无谷。故无策耳。盐之为用。与谷等。人之所需。不可一日而无之。自古赡国救民之术。以煮海为先。苟善措置。将取诸水而无穷。今 国家遭此无前之变。百物俱竭。更无着手处。独有此一事。为可讲求急行。故臣欲状启而未果。言于守城大将俞泓。使之驰启。未久。臣又南下。未知泓之果为启请。而 朝廷之见施与否。目今又见忠州等境。饥困
尽。极可哀痛。然其道内列色。已无储峙。无推移赈救之策。只有煮盐一事。稍可施行。臣前在京城。闻军资副正尹先民谙悉盐事。招见问计。先民云。黄海道丰川,瓮津,长渊三邑之境。有三四海岛。岛中杂木蓊郁。若伐木为薪。招集近处盐户及牧子等。使之煮取。则一盆一日所煮。可得五石盐。官取其半。而半与其煮盐之民。公私兼济。使之乐就。旬月之间。数万石盐。可以取办。因收聚公私船只之隐漏于海边者。亦以盐石给直。多数载船。散俵于两湖海边之今年农事颇稔处。随便换谷。而稍下其直。令民乐趋。勿论两麦木麦大小豆杂谷。随民间所有而贸之。移转于京江。赈救京城之民。以其馀。分给于开城各官。以为春秋种子。则其利甚博云云。其言甚似可行。臣因此思量。古语云。救荒无善策。盖以无谷。故无策耳。盐之为用。与谷等。人之所需。不可一日而无之。自古赡国救民之术。以煮海为先。苟善措置。将取诸水而无穷。今 国家遭此无前之变。百物俱竭。更无着手处。独有此一事。为可讲求急行。故臣欲状启而未果。言于守城大将俞泓。使之驰启。未久。臣又南下。未知泓之果为启请。而 朝廷之见施与否。目今又见忠州等境。饥困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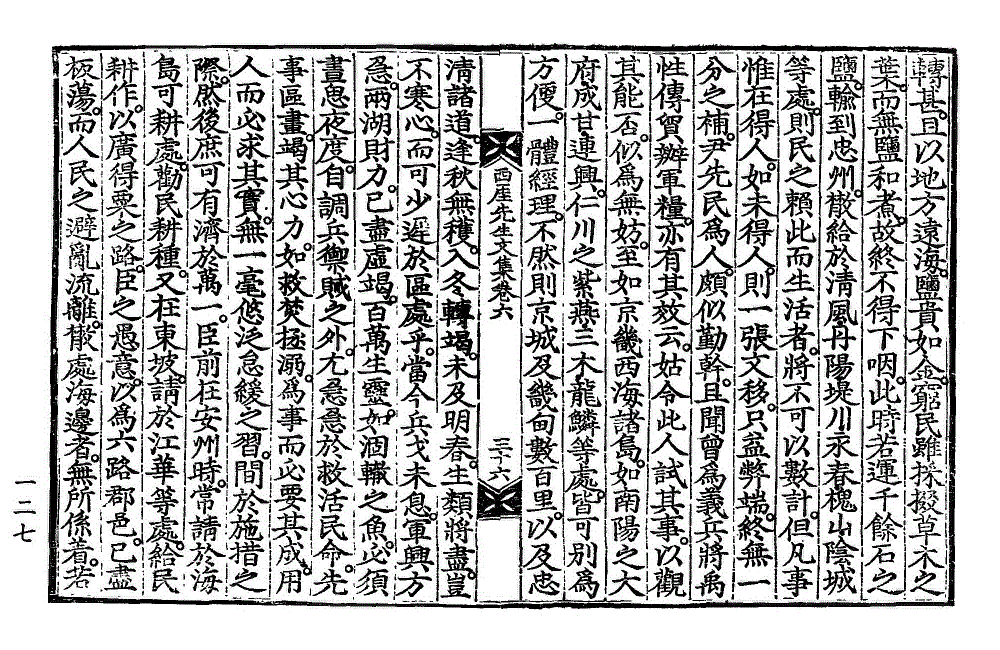 转甚。且以地方远海。盐贵如金。穷民虽采掇草木之叶。而无盐和煮。故终不得下咽。此时若运千馀石之盐。输到忠州。散给于清风,丹阳,堤川,永春,槐山,阴城等处。则民之赖此而生活者。将不可以数计。但凡事惟在得人。如未得人。则一张文移。只益弊端。终无一分之补。尹先民为人。颇似勤干。且闻曾为义兵将禹性传贸办军粮。亦有其效云。姑令此人试其事。以观其能否。似为无妨。至如京畿西海诸岛。如南阳之大府,成甘,连兴。仁川之紫燕,三木,龙鳞等处。皆可别为方便。一体经理。不然则京城及畿甸数百里。以及忠清诸道。逢秋无穫。入冬转竭。未及明春。生类将尽。岂不寒心。而可少迟于区处乎。当今兵戈未息。军兴方急。两湖财力。已尽处竭。百万生灵。如涸辙之鱼。必须昼思夜度。自调兵御贼之外。尤急急于救活民命。先事区画。竭其心力。如救焚拯溺。为事而必要其成。用人而必求其实。无一毫悠泛怠缓之习。间于施措之际。然后庶可有济于万一。臣前在安州时。常请于海岛可耕处。劝民耕种。又在东坡。请于江华等处。给民耕作。以广得粟之路。臣之愚意。以为六路郡邑。已尽板荡。而人民之避乱流离。散处海边者。无所系着。若
转甚。且以地方远海。盐贵如金。穷民虽采掇草木之叶。而无盐和煮。故终不得下咽。此时若运千馀石之盐。输到忠州。散给于清风,丹阳,堤川,永春,槐山,阴城等处。则民之赖此而生活者。将不可以数计。但凡事惟在得人。如未得人。则一张文移。只益弊端。终无一分之补。尹先民为人。颇似勤干。且闻曾为义兵将禹性传贸办军粮。亦有其效云。姑令此人试其事。以观其能否。似为无妨。至如京畿西海诸岛。如南阳之大府,成甘,连兴。仁川之紫燕,三木,龙鳞等处。皆可别为方便。一体经理。不然则京城及畿甸数百里。以及忠清诸道。逢秋无穫。入冬转竭。未及明春。生类将尽。岂不寒心。而可少迟于区处乎。当今兵戈未息。军兴方急。两湖财力。已尽处竭。百万生灵。如涸辙之鱼。必须昼思夜度。自调兵御贼之外。尤急急于救活民命。先事区画。竭其心力。如救焚拯溺。为事而必要其成。用人而必求其实。无一毫悠泛怠缓之习。间于施措之际。然后庶可有济于万一。臣前在安州时。常请于海岛可耕处。劝民耕种。又在东坡。请于江华等处。给民耕作。以广得粟之路。臣之愚意。以为六路郡邑。已尽板荡。而人民之避乱流离。散处海边者。无所系着。若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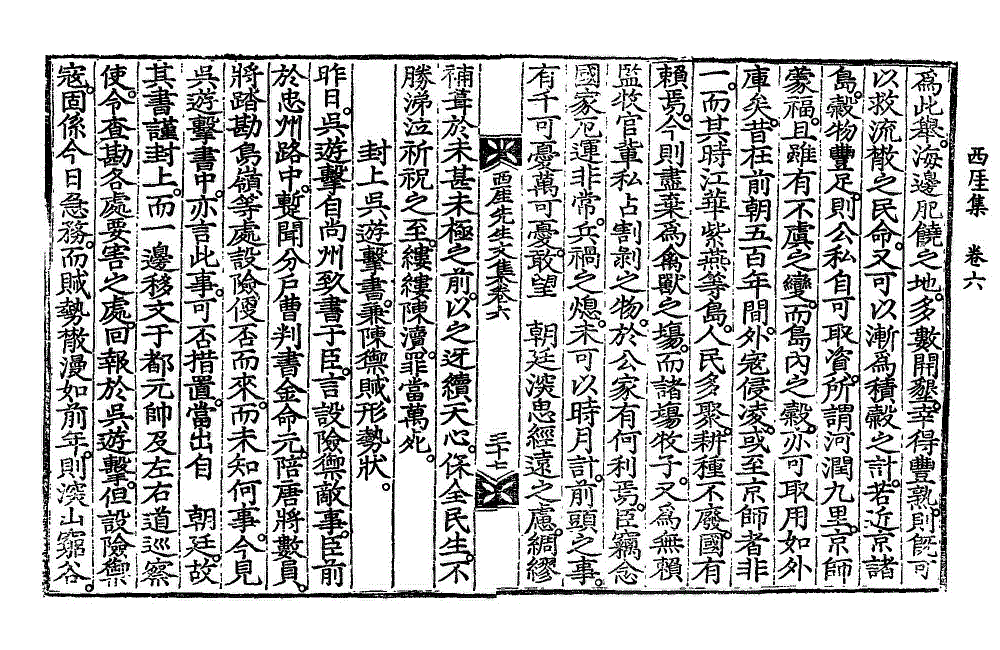 为此举。海边肥饶之地。多数开垦。幸得丰熟。则既可以救流散之民命。又可以渐为积谷之计。若近京诸岛。谷物丰足。则公私自可取资。所谓河润九里。京师蒙福。且虽有不虞之变。而岛内之谷。亦可取用如外库矣。昔在前朝五百年间。外寇侵凌。或至京师者非一。而其时江华紫燕等岛。人民多聚。耕种不废。国有赖焉。今则尽弃为禽兽之场。而诸场牧子。又为无赖监牧官辈私占割剥之物。于公家有何利焉。臣窃念国家厄运非常。兵祸之熄。未可以时月计。前头之事。有千可忧万可忧。敢望 朝廷深思经远之虑。绸缪补葺于未甚未极之前。以之迓续天心。保全民生。不胜悌泣祈祝之至。缕缕陈渎。罪当万死。
为此举。海边肥饶之地。多数开垦。幸得丰熟。则既可以救流散之民命。又可以渐为积谷之计。若近京诸岛。谷物丰足。则公私自可取资。所谓河润九里。京师蒙福。且虽有不虞之变。而岛内之谷。亦可取用如外库矣。昔在前朝五百年间。外寇侵凌。或至京师者非一。而其时江华紫燕等岛。人民多聚。耕种不废。国有赖焉。今则尽弃为禽兽之场。而诸场牧子。又为无赖监牧官辈私占割剥之物。于公家有何利焉。臣窃念国家厄运非常。兵祸之熄。未可以时月计。前头之事。有千可忧万可忧。敢望 朝廷深思经远之虑。绸缪补葺于未甚未极之前。以之迓续天心。保全民生。不胜悌泣祈祝之至。缕缕陈渎。罪当万死。封上吴游击书。兼陈御贼形势状。
昨日。吴游击自尚州致书于臣。言设险御敌事。臣前于忠州路中。暂闻分户曹判书金命元。陪唐将数员。将踏勘鸟岭等处设险便否而来。而未知何事。今见吴游击书中。亦言此事。可否措置。当出自 朝廷。故其书谨封上。而一边移文于都元帅及左右道巡察使。令查勘各处要害之处。回报于吴游击。但设险御寇。固系今日急务。而贼势散漫如前年。则深山穷谷。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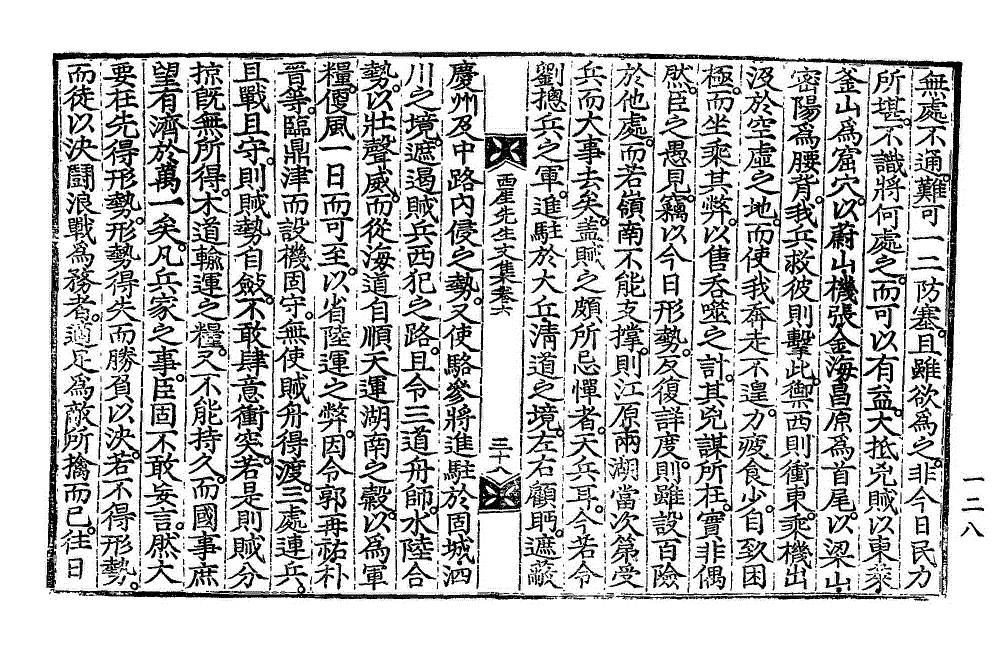 无处不通。难可一二防塞。且虽欲为之。非今日民力所堪。不识将何处之。而可以有益。大抵凶贼以东莱,釜山为窟穴。以蔚山,机张,金海,昌原为首尾。以梁山,密阳为腰背。我兵救彼则击此。御西则冲东。乘机出没于空虚之地。而使我奔走不遑。力疲食少。自致困极。而坐乘其弊。以售吞噬之计。其凶谋所在。实非偶然。臣之愚见。窃以今日形势。反复详度。则虽设百险于他处。而若岭南不能支撑。则江原,两湖当次第受兵而大事去矣。盖贼之颇所忌惮者。天兵耳。今若令刘总兵之军。进驻于大丘,清道之境。左右顾眄。遮蔽庆州及中路内侵之势。又使骆参将进驻于固城,泗川之境。遮遏贼兵西犯之路。且令三道舟师。水陆合势。以壮声威。而从海道自顺天运湖南之谷。以为军粮。便风一日而可至。以省陆运之弊。因令郭再祐,朴晋等。临鼎津而设机固守。无使贼舟得渡。三处连兵。且战且守。则贼势自敛。不敢肆意冲突。若是则贼分掠既无所得。木道输运之粮。又不能持久。而国事庶望有济于万一矣。凡兵家之事。臣固不敢妄言。然大要在先得形势。形势得失而胜负以决。若不得形势。而徒以决斗浪战为务者。适足为敌所擒而已。往日
无处不通。难可一二防塞。且虽欲为之。非今日民力所堪。不识将何处之。而可以有益。大抵凶贼以东莱,釜山为窟穴。以蔚山,机张,金海,昌原为首尾。以梁山,密阳为腰背。我兵救彼则击此。御西则冲东。乘机出没于空虚之地。而使我奔走不遑。力疲食少。自致困极。而坐乘其弊。以售吞噬之计。其凶谋所在。实非偶然。臣之愚见。窃以今日形势。反复详度。则虽设百险于他处。而若岭南不能支撑。则江原,两湖当次第受兵而大事去矣。盖贼之颇所忌惮者。天兵耳。今若令刘总兵之军。进驻于大丘,清道之境。左右顾眄。遮蔽庆州及中路内侵之势。又使骆参将进驻于固城,泗川之境。遮遏贼兵西犯之路。且令三道舟师。水陆合势。以壮声威。而从海道自顺天运湖南之谷。以为军粮。便风一日而可至。以省陆运之弊。因令郭再祐,朴晋等。临鼎津而设机固守。无使贼舟得渡。三处连兵。且战且守。则贼势自敛。不敢肆意冲突。若是则贼分掠既无所得。木道输运之粮。又不能持久。而国事庶望有济于万一矣。凡兵家之事。臣固不敢妄言。然大要在先得形势。形势得失而胜负以决。若不得形势。而徒以决斗浪战为务者。适足为敌所擒而已。往日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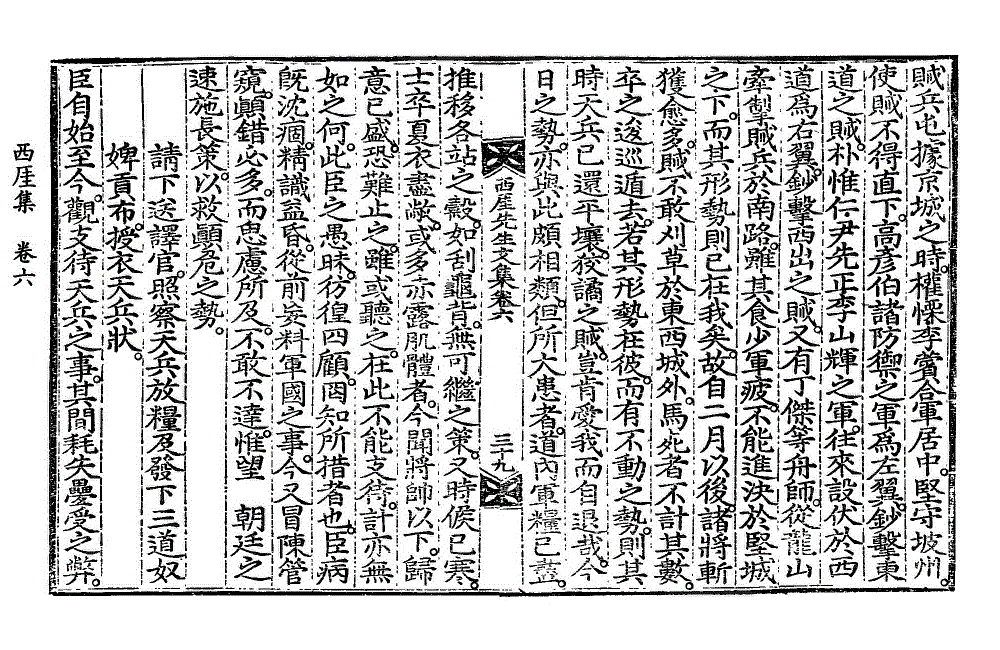 贼兵屯据京城之时。权慄,李蘋合军居中。坚守坡州。使贼不得直下。高彦伯诸防御之军为左翼。钞击东道之贼。朴惟仁,尹先正,李山辉之军。往来设伏于西道为右翼。钞击西出之贼。又有丁杰等舟师。从龙山牵掣贼兵于南路。虽其食少军疲。不能进决于坚城之下。而其形势则已在我矣。故自二月以后。诸将斩获愈多。贼不敢刈草于东西城外。马死者不计其数。卒之逡巡遁去。若其形势在彼。而有不动之势。则其时天兵已还平壤。狡谲之贼。岂肯爱我而自退哉。今日之势。亦与此颇相类。但所大患者。道内军粮已尽。推移各站之谷。如刮龟背。无可继之策。又时候已寒。士卒夏衣尽敝。或多赤露肌体者。今闻将帅以下。归意已盛。恐难止之。虽或听之。在此不能支待。计亦无如之何。此臣之愚昧。彷徨四顾。罔知所措者也。臣病既沈痼。精识益昏。从前妄料军国之事。今又昌陈管窥。颠错必多。而思虑所及。不敢不达。惟望 朝廷之速施长策。以救颠危之势。
贼兵屯据京城之时。权慄,李蘋合军居中。坚守坡州。使贼不得直下。高彦伯诸防御之军为左翼。钞击东道之贼。朴惟仁,尹先正,李山辉之军。往来设伏于西道为右翼。钞击西出之贼。又有丁杰等舟师。从龙山牵掣贼兵于南路。虽其食少军疲。不能进决于坚城之下。而其形势则已在我矣。故自二月以后。诸将斩获愈多。贼不敢刈草于东西城外。马死者不计其数。卒之逡巡遁去。若其形势在彼。而有不动之势。则其时天兵已还平壤。狡谲之贼。岂肯爱我而自退哉。今日之势。亦与此颇相类。但所大患者。道内军粮已尽。推移各站之谷。如刮龟背。无可继之策。又时候已寒。士卒夏衣尽敝。或多赤露肌体者。今闻将帅以下。归意已盛。恐难止之。虽或听之。在此不能支待。计亦无如之何。此臣之愚昧。彷徨四顾。罔知所措者也。臣病既沈痼。精识益昏。从前妄料军国之事。今又昌陈管窥。颠错必多。而思虑所及。不敢不达。惟望 朝廷之速施长策。以救颠危之势。请下送译官。照察天兵放粮及发下三道奴婢贡布。授衣天兵状。
臣自始至今。观支待天兵之事。其间耗失叠受之弊。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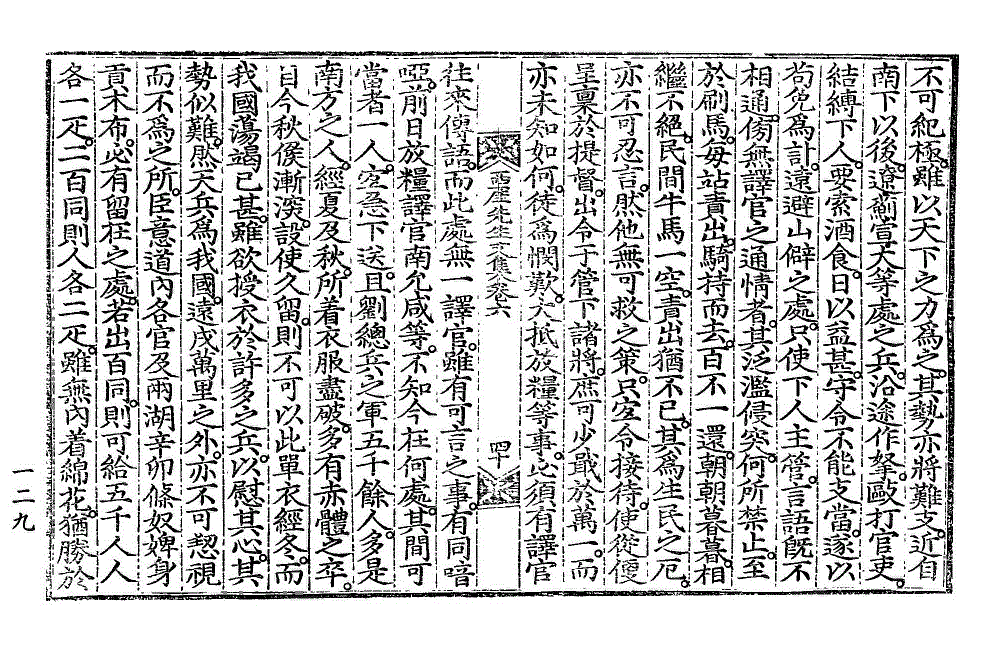 不可纪极。虽以天下之力为之。其势亦将难支。近自南下以后。辽,蓟,宣,大等处之兵。沿途作拿。驱打官吏。结缚下人。要索酒食。日以益甚。守令不能支当。遂以苟免为计。远避山僻之处。只使下人主管。言语既不相通。傍无译官之通情者。其泛滥侵突。何所禁止。至于刷马。每站责出。骑持而去。百不一还。朝朝暮暮。相继不绝。民间牛马一空。责出犹不已。其为生民之厄。亦不可忍言。然他无可救之策。只宜令接待。使从便呈禀于提督。出令于管下诸将。庶可少戢于万一。而亦未知如何。徒为悯叹。大抵放粮等事。必须有译官往来传语。而此处无一译官。虽有可言之事。有同喑哑。前日放粮译官南允咸等。不知今在何处。其间可当者一人。宜急下送。且刘总兵之军五千馀人。多是南方之人。经夏及秋。所着衣服尽破。多有赤体之卒。目今秋候渐深。设使久留。则不可以此单衣经冬。而我国荡竭已甚。虽欲授衣于许多之兵。以慰其心。其势似难。然天兵为我国。远戍万里之外。亦不可恝视而不为之所。臣意道内各官及两湖辛卯条奴婢身贡木布。必有留在之处。若出百同。则可给五千人人各一疋。二百同则人各二疋。虽无内着绵花。犹胜于
不可纪极。虽以天下之力为之。其势亦将难支。近自南下以后。辽,蓟,宣,大等处之兵。沿途作拿。驱打官吏。结缚下人。要索酒食。日以益甚。守令不能支当。遂以苟免为计。远避山僻之处。只使下人主管。言语既不相通。傍无译官之通情者。其泛滥侵突。何所禁止。至于刷马。每站责出。骑持而去。百不一还。朝朝暮暮。相继不绝。民间牛马一空。责出犹不已。其为生民之厄。亦不可忍言。然他无可救之策。只宜令接待。使从便呈禀于提督。出令于管下诸将。庶可少戢于万一。而亦未知如何。徒为悯叹。大抵放粮等事。必须有译官往来传语。而此处无一译官。虽有可言之事。有同喑哑。前日放粮译官南允咸等。不知今在何处。其间可当者一人。宜急下送。且刘总兵之军五千馀人。多是南方之人。经夏及秋。所着衣服尽破。多有赤体之卒。目今秋候渐深。设使久留。则不可以此单衣经冬。而我国荡竭已甚。虽欲授衣于许多之兵。以慰其心。其势似难。然天兵为我国。远戍万里之外。亦不可恝视而不为之所。臣意道内各官及两湖辛卯条奴婢身贡木布。必有留在之处。若出百同。则可给五千人人各一疋。二百同则人各二疋。虽无内着绵花。犹胜于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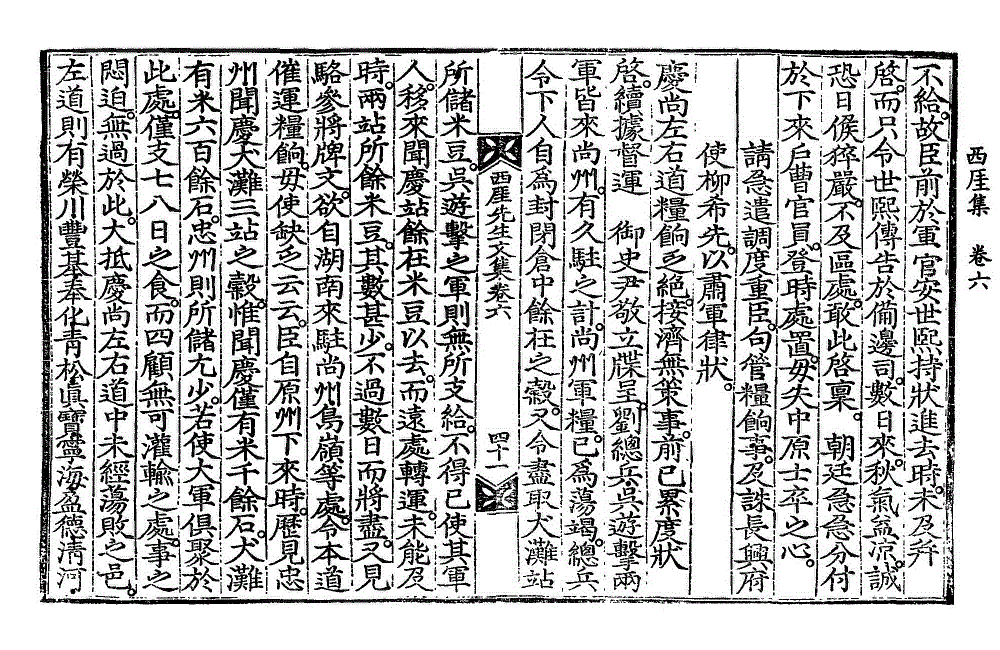 不给。故臣前于军官安世熙持状进去时。未及并 启。而只令世熙传告于备边司。数日来。秋气益凉。诚恐日候猝严。不及区处。敢此启禀。 朝廷急急分付于下来户曹官员。登时处置。毋失中原士卒之心。
不给。故臣前于军官安世熙持状进去时。未及并 启。而只令世熙传告于备边司。数日来。秋气益凉。诚恐日候猝严。不及区处。敢此启禀。 朝廷急急分付于下来户曹官员。登时处置。毋失中原士卒之心。请急遣调度重臣。句管粮饷事。及诛长兴府使柳希先。以肃军律状。
庆尚左右道粮饷乏绝。接济无策事。前已累度状 启。续据督运 御史尹敬立牒呈。刘总兵,吴游击两军皆来尚州。有久驻之计。尚州军粮。已为荡竭。总兵令下人自为封闭仓中馀在之谷。又令尽取犬滩站所储米豆。吴游击之军则无所支给。不得已使其军人。移来闻庆站馀在米豆以去。而远处转运。未能及时。两站所馀米豆。其数甚少。不过数日而将尽。又见骆参将牌文。欲自湖南来驻尚州,鸟岭等处。令本道催运粮饷。毋使缺乏云云。臣自原州下来时。历见忠州,闻庆,犬滩三站之谷。惟闻庆仅有米千馀石。犬滩有米六百馀石。忠州则所储尤少。若使大军俱聚于此处。仅支七八日之食。而四顾无可灌输之处。事之闷迫。无过于此。大抵庆尚左右道中未经荡败之邑。左道则有荣川,丰基,奉化,青松,真宝,宁海,盈德,清河,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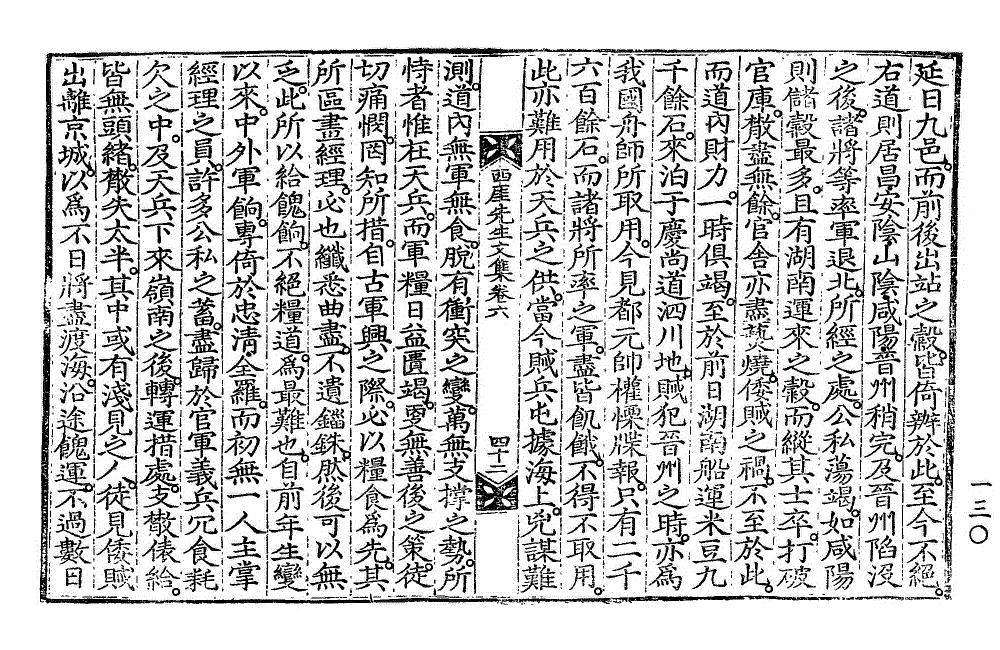 延日九邑。而前后出站之谷。皆倚办于此。至今不绝。右道则居昌,安阴,山阴,咸阳,晋州稍完。及晋州陷没之后。诸将等率军退北。所经之处。公私荡竭。如咸阳则储谷最多。且有湖南运来之谷。而纵其士卒。打破官库。散尽无馀。官舍亦尽爇烧。倭贼之祸。不至于此。而道内财力。一时俱竭。至于前日湖南船运米豆九千馀石。来泊于庆尚道泗川地。贼犯晋州之时。亦为我国舟师所取用。今见都元帅权慄牒报。只有二千六百馀石。而诸将所率之军。尽皆饥饿。不得不取用。此亦难用于天兵之供。当今贼兵屯据海上。凶谋难测。道内无军无食。脱有冲突之变。万无支撑之势。所恃者惟在天兵。而军粮日益匮竭。更无善后之策。徒切痛悯。罔知所措。自古军兴之际。必以粮食为先。其所区画经理。必也纤悉曲尽。不遗锱铢。然后可以无乏。此所以给馈饷。不绝粮道。为最难也。自前年生变以来。中外军饷。专倚于忠清,全罗。而初无一人主掌经理之员。许多公私之蓄。尽归于官军义兵冗食耗欠之中。及天兵下来岭南之后。转运措处。支散俵给。皆无头绪。散失太半。其中或有浅见之人。徒见倭贼出离京城。以为不日将尽渡海。沿途馈运。不过数日
延日九邑。而前后出站之谷。皆倚办于此。至今不绝。右道则居昌,安阴,山阴,咸阳,晋州稍完。及晋州陷没之后。诸将等率军退北。所经之处。公私荡竭。如咸阳则储谷最多。且有湖南运来之谷。而纵其士卒。打破官库。散尽无馀。官舍亦尽爇烧。倭贼之祸。不至于此。而道内财力。一时俱竭。至于前日湖南船运米豆九千馀石。来泊于庆尚道泗川地。贼犯晋州之时。亦为我国舟师所取用。今见都元帅权慄牒报。只有二千六百馀石。而诸将所率之军。尽皆饥饿。不得不取用。此亦难用于天兵之供。当今贼兵屯据海上。凶谋难测。道内无军无食。脱有冲突之变。万无支撑之势。所恃者惟在天兵。而军粮日益匮竭。更无善后之策。徒切痛悯。罔知所措。自古军兴之际。必以粮食为先。其所区画经理。必也纤悉曲尽。不遗锱铢。然后可以无乏。此所以给馈饷。不绝粮道。为最难也。自前年生变以来。中外军饷。专倚于忠清,全罗。而初无一人主掌经理之员。许多公私之蓄。尽归于官军义兵冗食耗欠之中。及天兵下来岭南之后。转运措处。支散俵给。皆无头绪。散失太半。其中或有浅见之人。徒见倭贼出离京城。以为不日将尽渡海。沿途馈运。不过数日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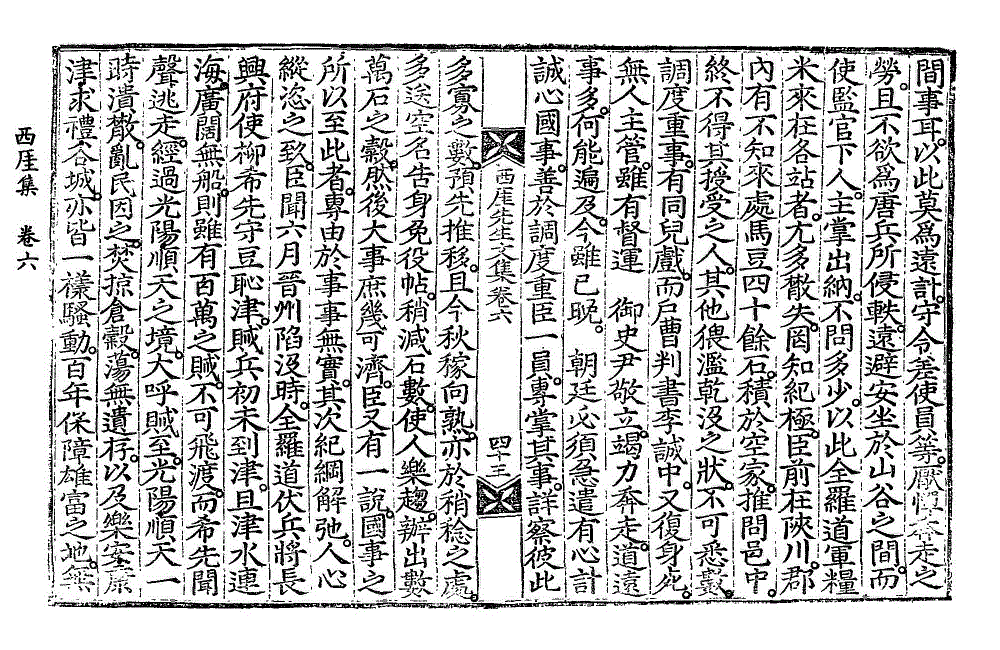 间事耳。以此莫为远计。守令差使员等。厌惮奔走之劳。且不欲为唐兵所侵轶。远避安坐于山谷之间。而使监官下人。主掌出纳。不问多少。以此全罗道军粮米来在各站者。尤多散失。罔知纪极。臣前在陜川。郡内有不知来处马豆四十馀石。积于空家。推问邑中。终不得其授受之人。其他猥滥乾没之状。不可悉数。调度重事。有同儿戏。而户曹判书李诚中。又复身死。无人主管。虽有督运 御史尹敬立。竭力奔走。道远事多。何能遍及。今虽已晚。 朝廷必须急遣有心计诚心国事。善于调度重臣一员。专掌其事。详察彼此多寡之数。预先推移。且今秋稼向熟。亦于稍稔之处。多送空名告身免役帖。稍减石数。使人乐趋。办出数万石之谷。然后大事庶几可济。臣又有一说。国事之所以至此者。专由于事事无实。其次纪纲解弛。人心纵恣之致。臣闻六月晋州陷没时。全罗道伏兵将长兴府使柳希先守豆耻津。贼兵初未到津。且津水连海。广阔无船。则虽有百万之贼。不可飞渡。而希先闻声逃走。经过光阳,顺天之境。大呼贼至。光阳,顺天一时溃散。乱民因之。焚掠仓谷。荡无遗存。以及乐安,康津,求礼,谷城。亦皆一样骚动。百年保障雄富之地。无
间事耳。以此莫为远计。守令差使员等。厌惮奔走之劳。且不欲为唐兵所侵轶。远避安坐于山谷之间。而使监官下人。主掌出纳。不问多少。以此全罗道军粮米来在各站者。尤多散失。罔知纪极。臣前在陜川。郡内有不知来处马豆四十馀石。积于空家。推问邑中。终不得其授受之人。其他猥滥乾没之状。不可悉数。调度重事。有同儿戏。而户曹判书李诚中。又复身死。无人主管。虽有督运 御史尹敬立。竭力奔走。道远事多。何能遍及。今虽已晚。 朝廷必须急遣有心计诚心国事。善于调度重臣一员。专掌其事。详察彼此多寡之数。预先推移。且今秋稼向熟。亦于稍稔之处。多送空名告身免役帖。稍减石数。使人乐趋。办出数万石之谷。然后大事庶几可济。臣又有一说。国事之所以至此者。专由于事事无实。其次纪纲解弛。人心纵恣之致。臣闻六月晋州陷没时。全罗道伏兵将长兴府使柳希先守豆耻津。贼兵初未到津。且津水连海。广阔无船。则虽有百万之贼。不可飞渡。而希先闻声逃走。经过光阳,顺天之境。大呼贼至。光阳,顺天一时溃散。乱民因之。焚掠仓谷。荡无遗存。以及乐安,康津,求礼,谷城。亦皆一样骚动。百年保障雄富之地。无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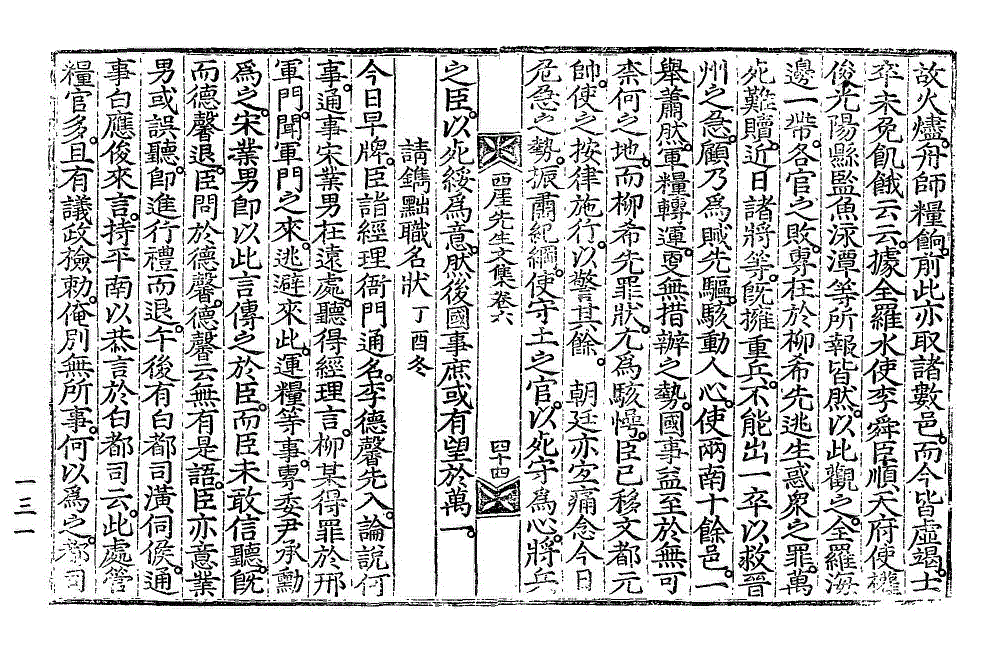 故火烬。舟师粮饷。前此亦取诸数邑。而今皆虚竭。士卒未免饥饿云云。据全罗水使李舜臣,顺天府使权俊,光阳县监鱼泳潭等所报皆然。以此观之。全罗海边一带。各官之败。专在于柳希先逃生惑众之罪。万死难赎。近日诸将等。既拥重兵。不能出一卒以救晋州之急。顾乃为贼先驱。骇动人心。使两南十馀邑。一举萧然。军粮转运。更无措办之势。国事益至于无可柰何之地。而柳希先罪状。尤为骇愕。臣已移文都元帅。使之按律施行。以警其馀。 朝廷亦宜痛念今日危急之势。振肃纪纲。使守土之官。以死守为心。将兵之臣。以死绥为意。然后国事庶或有望于万一。
故火烬。舟师粮饷。前此亦取诸数邑。而今皆虚竭。士卒未免饥饿云云。据全罗水使李舜臣,顺天府使权俊,光阳县监鱼泳潭等所报皆然。以此观之。全罗海边一带。各官之败。专在于柳希先逃生惑众之罪。万死难赎。近日诸将等。既拥重兵。不能出一卒以救晋州之急。顾乃为贼先驱。骇动人心。使两南十馀邑。一举萧然。军粮转运。更无措办之势。国事益至于无可柰何之地。而柳希先罪状。尤为骇愕。臣已移文都元帅。使之按律施行。以警其馀。 朝廷亦宜痛念今日危急之势。振肃纪纲。使守土之官。以死守为心。将兵之臣。以死绥为意。然后国事庶或有望于万一。请镌黜职名状(丁酉冬)
今日早牌。臣诣经理衙门通名。李德馨先入。论说何事。通事宋业男在远处。听得经理言。柳某得罪于邢军门。闻军门之来。逃避来此。运粮等事。专委尹承勋为之。宋业男即以此言传之于臣。而臣未敢信听。既而德馨退。臣问于德馨。德馨云无有是语。臣亦意业男或误听。即进行礼而退。午后有白都司潢伺候。通事白应俊来言。持平南以恭言于白都司云。此处管粮官多。且有议政检敕。俺别无所事。何以为之。都司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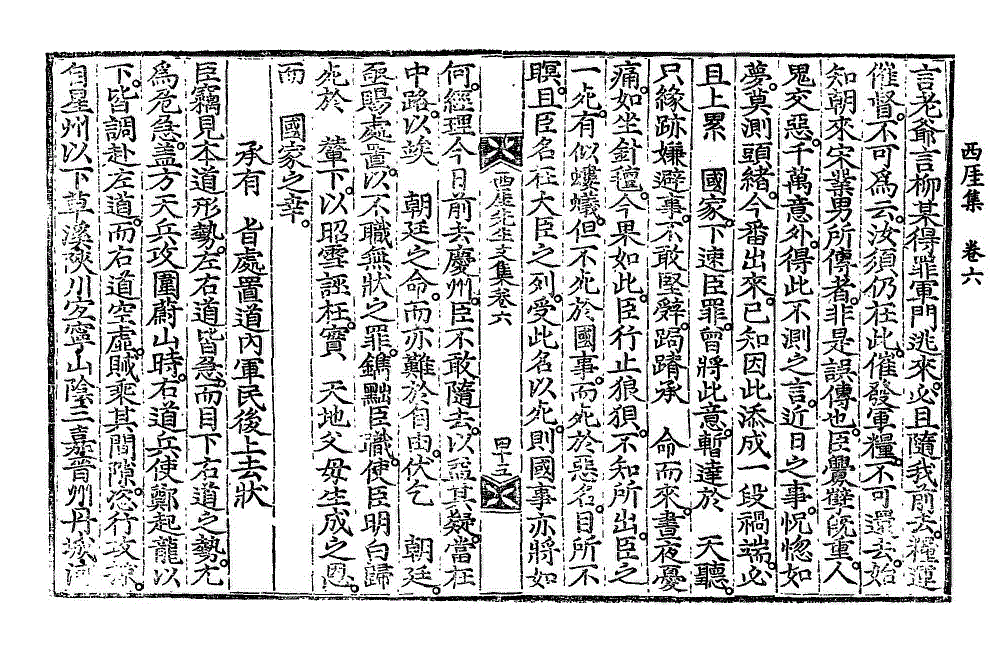 言老爷言柳某得罪军门逃来。必且随我前去。粮运催督。不可为云。汝须仍在此。催发军粮。不可还去。始知朝来宋业男所传者。非是误传也。臣衅孽既重。人鬼交恶。千万意外。得此不测之言。近日之事。恍惚如梦。莫测头绪。今番出来。已知因此添成一段祸端。必且上累 国家。下速臣罪。曾将此意。暂达于 天听。只缘迹嫌避事。不敢坚辞。跼蹐承 命而来。昼夜忧痛。如坐针毡。今果如此。臣行止狼狈。不知所出。臣之一死。有似蝼蚁。但不死于国事。而死于恶名。目所不瞑。且臣名在大臣之列。受此名以死。则国事亦将如何。经理今日前去庆州。臣不敢随去。以益其疑。当在中路。以俟 朝廷之命。而亦难于自由。伏乞 朝廷。亟赐处置。以不职无状之罪。镌黜臣职。使臣明白归死于 辇下。以昭雪诬枉。实 天地父母生成之恩。而 国家之幸。
言老爷言柳某得罪军门逃来。必且随我前去。粮运催督。不可为云。汝须仍在此。催发军粮。不可还去。始知朝来宋业男所传者。非是误传也。臣衅孽既重。人鬼交恶。千万意外。得此不测之言。近日之事。恍惚如梦。莫测头绪。今番出来。已知因此添成一段祸端。必且上累 国家。下速臣罪。曾将此意。暂达于 天听。只缘迹嫌避事。不敢坚辞。跼蹐承 命而来。昼夜忧痛。如坐针毡。今果如此。臣行止狼狈。不知所出。臣之一死。有似蝼蚁。但不死于国事。而死于恶名。目所不瞑。且臣名在大臣之列。受此名以死。则国事亦将如何。经理今日前去庆州。臣不敢随去。以益其疑。当在中路。以俟 朝廷之命。而亦难于自由。伏乞 朝廷。亟赐处置。以不职无状之罪。镌黜臣职。使臣明白归死于 辇下。以昭雪诬枉。实 天地父母生成之恩。而 国家之幸。承有 旨处置道内军民后上去状
臣窃见本道形势。左右道皆急。而目下右道之势。尤为危急。盖方天兵攻围蔚山时。右道兵使郑起龙以下。皆调赴左道。而右道空虚。贼乘其间隙。恣行攻掠。自星州以下草溪,陜川,宜宁,山阴,三嘉,晋州,丹城,河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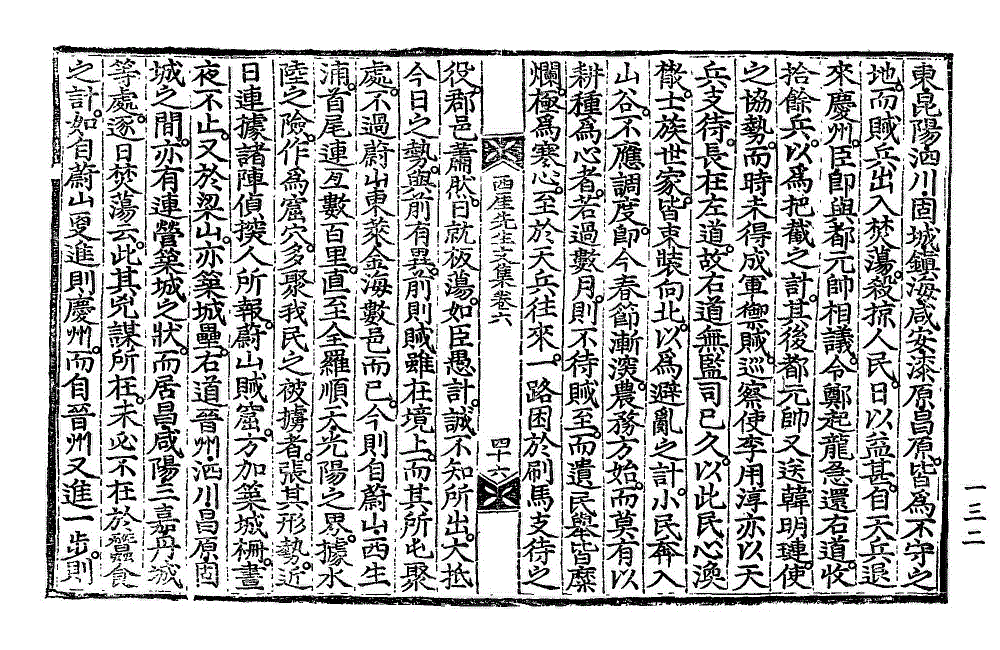 东,昆阳,泗川,固城,镇海,咸安,漆原,昌原。皆为不守之地。而贼兵出入焚荡。杀掠人民。日以益甚。自天兵退来庆州。臣即与都元帅相议。令郑起龙急还右道。收拾馀兵。以为把截之计。其后都元帅又送韩明琏。使之协势。而时未得成军御贼。巡察使李用淳亦以天兵支待。长在左道。故右道无监司已久。以此民心涣散。士族世家。皆束装向北。以为避乱之计。小民奔入山谷。不应调度。即今春节渐深。农务方始。而莫有以耕种为心者。若过数月。则不待贼至。而遗民举皆糜烂。极为寒心。至于天兵往来。一路困于刷马支待之役。郡邑萧然。日就板荡。如臣愚计。诚不知所出。大抵今日之势。与前有异。前则贼虽在境上。而其所屯聚处。不过蔚山,东莱,金海数邑而已。今则自蔚山,西生浦。首尾连亘数百里。直至全罗顺天,光阳之界。据水陆之险。作为窟穴。多聚我民之被掳者。张其形势。近日连据诸阵侦探人所报。蔚山贼窟。方加筑城栅。昼夜不止。又于梁山。亦筑城垒。右道晋州,泗川,昌原,固城之间。亦有连营筑城之状。而居昌,咸阳,三嘉,丹城等处。逐日焚荡云。此其凶谋所在。未必不在于蚕食之计。如自蔚山更进则庆州。而自晋州又进一步。则
东,昆阳,泗川,固城,镇海,咸安,漆原,昌原。皆为不守之地。而贼兵出入焚荡。杀掠人民。日以益甚。自天兵退来庆州。臣即与都元帅相议。令郑起龙急还右道。收拾馀兵。以为把截之计。其后都元帅又送韩明琏。使之协势。而时未得成军御贼。巡察使李用淳亦以天兵支待。长在左道。故右道无监司已久。以此民心涣散。士族世家。皆束装向北。以为避乱之计。小民奔入山谷。不应调度。即今春节渐深。农务方始。而莫有以耕种为心者。若过数月。则不待贼至。而遗民举皆糜烂。极为寒心。至于天兵往来。一路困于刷马支待之役。郡邑萧然。日就板荡。如臣愚计。诚不知所出。大抵今日之势。与前有异。前则贼虽在境上。而其所屯聚处。不过蔚山,东莱,金海数邑而已。今则自蔚山,西生浦。首尾连亘数百里。直至全罗顺天,光阳之界。据水陆之险。作为窟穴。多聚我民之被掳者。张其形势。近日连据诸阵侦探人所报。蔚山贼窟。方加筑城栅。昼夜不止。又于梁山。亦筑城垒。右道晋州,泗川,昌原,固城之间。亦有连营筑城之状。而居昌,咸阳,三嘉,丹城等处。逐日焚荡云。此其凶谋所在。未必不在于蚕食之计。如自蔚山更进则庆州。而自晋州又进一步。则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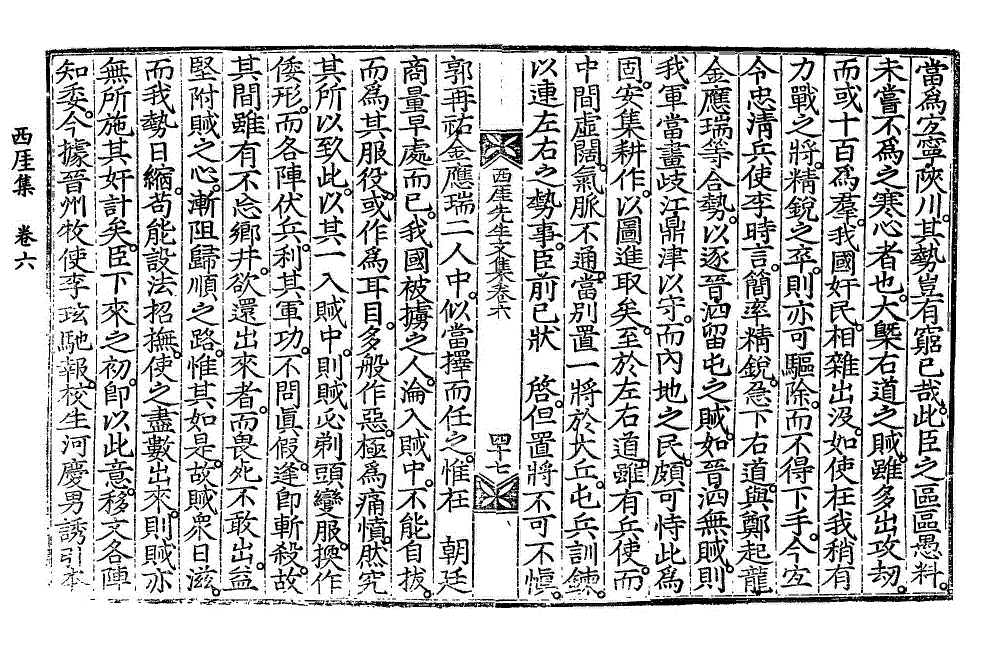 当为宜宁,陜川。其势岂有穷已哉。此臣之区区愚料。未尝不为之寒心者也。大槩右道之贼。虽多出攻劫。而或十百为群。我国奸民。相杂出没。如使在我稍有力战之将。精锐之卒。则亦可驱除。而不得下手。今宜令忠清兵使李时言。简率精锐。急下右道。与郑起龙,金应瑞等合势。以逐晋,泗留屯之贼。如晋,泗无贼。则我军当画歧江,鼎津以守。而内地之民。颇可恃此为固。安集耕作。以图进取矣。至于左右道。虽有兵使。而中间虚阔。气脉不通。当别置一将于大丘。屯兵训鍊。以连左右之势事。臣前已状 启。但置将不可不慎。郭再祐,金应瑞二人中。似当择而任之。惟在 朝廷商量早处而已。我国被掳之人。沦入贼中。不能自拔。而为其服役。或作为耳目。多般作恶。极为痛愤。然究其所以致此。以其一入贼中。则贼必剃头变服。换作倭形。而各阵伏兵。利其军功。不问真假。逢即斩杀。故其间虽有不忘乡井。欲还出来者。而畏死不敢出。益坚附贼之心。渐阻归顺之路。惟其如是。故贼众日滋。而我势日缩。苟能设法招抚。使之尽数出来。则贼亦无所施其奸计矣。臣下来之初。即以此意。移文各阵知委。今据晋州牧使李玹驰报。校生河庆男诱引本
当为宜宁,陜川。其势岂有穷已哉。此臣之区区愚料。未尝不为之寒心者也。大槩右道之贼。虽多出攻劫。而或十百为群。我国奸民。相杂出没。如使在我稍有力战之将。精锐之卒。则亦可驱除。而不得下手。今宜令忠清兵使李时言。简率精锐。急下右道。与郑起龙,金应瑞等合势。以逐晋,泗留屯之贼。如晋,泗无贼。则我军当画歧江,鼎津以守。而内地之民。颇可恃此为固。安集耕作。以图进取矣。至于左右道。虽有兵使。而中间虚阔。气脉不通。当别置一将于大丘。屯兵训鍊。以连左右之势事。臣前已状 启。但置将不可不慎。郭再祐,金应瑞二人中。似当择而任之。惟在 朝廷商量早处而已。我国被掳之人。沦入贼中。不能自拔。而为其服役。或作为耳目。多般作恶。极为痛愤。然究其所以致此。以其一入贼中。则贼必剃头变服。换作倭形。而各阵伏兵。利其军功。不问真假。逢即斩杀。故其间虽有不忘乡井。欲还出来者。而畏死不敢出。益坚附贼之心。渐阻归顺之路。惟其如是。故贼众日滋。而我势日缩。苟能设法招抚。使之尽数出来。则贼亦无所施其奸计矣。臣下来之初。即以此意。移文各阵知委。今据晋州牧使李玹驰报。校生河庆男诱引本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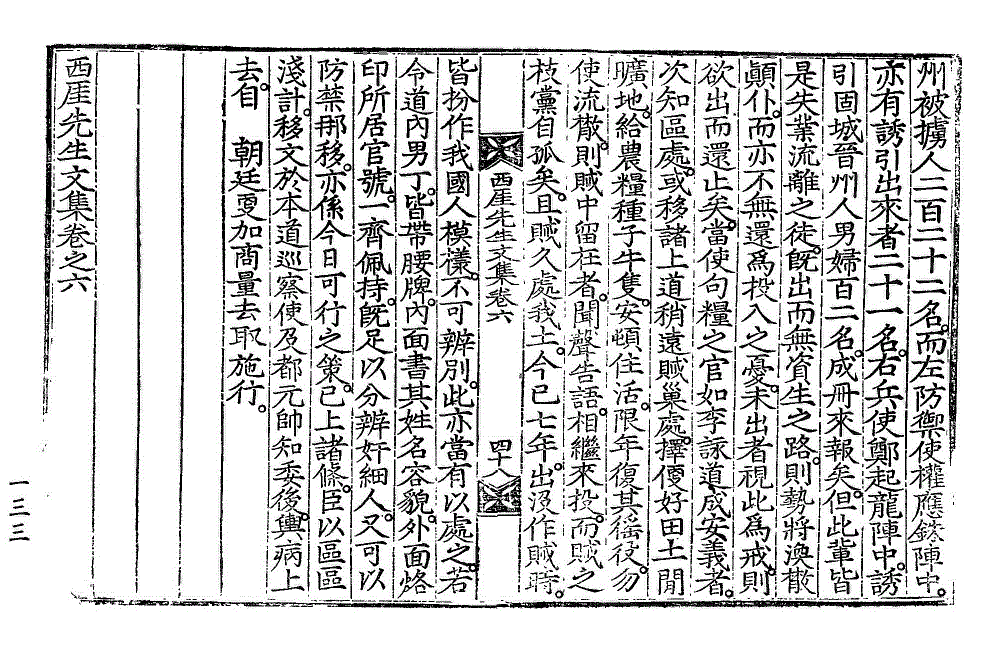 州被掳人二百二十二名。而左防御使权应铢阵中。亦有诱引出来者二十一名。右兵使郑起龙阵中。诱引固城,晋州人男妇百二名。成册来报矣。但此辈皆是失业流离之徒。既出而无资生之路。则势将涣散颠仆。而亦不无还为投入之忧。未出者视此为戒。则欲出而还止矣。当使句粮之官如李咏道,成安义者。次知区处。或移诸上道稍远贼巢处。择便好田土閒旷地。给农粮种子牛只。安顿住活。限年复其徭役。勿使流散。则贼中留在者。闻声告语。相继来投。而贼之枝党自孤矣。且贼久处我土。今已七年。出没作贼时。皆扮作我国人模样。不可辨别。此亦当有以处之。若令道内男丁。皆带腰牌。内面书其姓名容貌。外面烙印所居官号。一齐佩持。既足以分辨奸细人。又可以防禁那移。亦系今日可行之策。已上诸条。臣以区区浅计。移文于本道巡察使及都元帅知委后。舆病上去。自 朝廷更加商量去取施行。
州被掳人二百二十二名。而左防御使权应铢阵中。亦有诱引出来者二十一名。右兵使郑起龙阵中。诱引固城,晋州人男妇百二名。成册来报矣。但此辈皆是失业流离之徒。既出而无资生之路。则势将涣散颠仆。而亦不无还为投入之忧。未出者视此为戒。则欲出而还止矣。当使句粮之官如李咏道,成安义者。次知区处。或移诸上道稍远贼巢处。择便好田土閒旷地。给农粮种子牛只。安顿住活。限年复其徭役。勿使流散。则贼中留在者。闻声告语。相继来投。而贼之枝党自孤矣。且贼久处我土。今已七年。出没作贼时。皆扮作我国人模样。不可辨别。此亦当有以处之。若令道内男丁。皆带腰牌。内面书其姓名容貌。外面烙印所居官号。一齐佩持。既足以分辨奸细人。又可以防禁那移。亦系今日可行之策。已上诸条。臣以区区浅计。移文于本道巡察使及都元帅知委后。舆病上去。自 朝廷更加商量去取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