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四留斋集卷之六 第 x 页
四留斋集卷之六
疏劄
疏劄
四留斋集卷之六 第 3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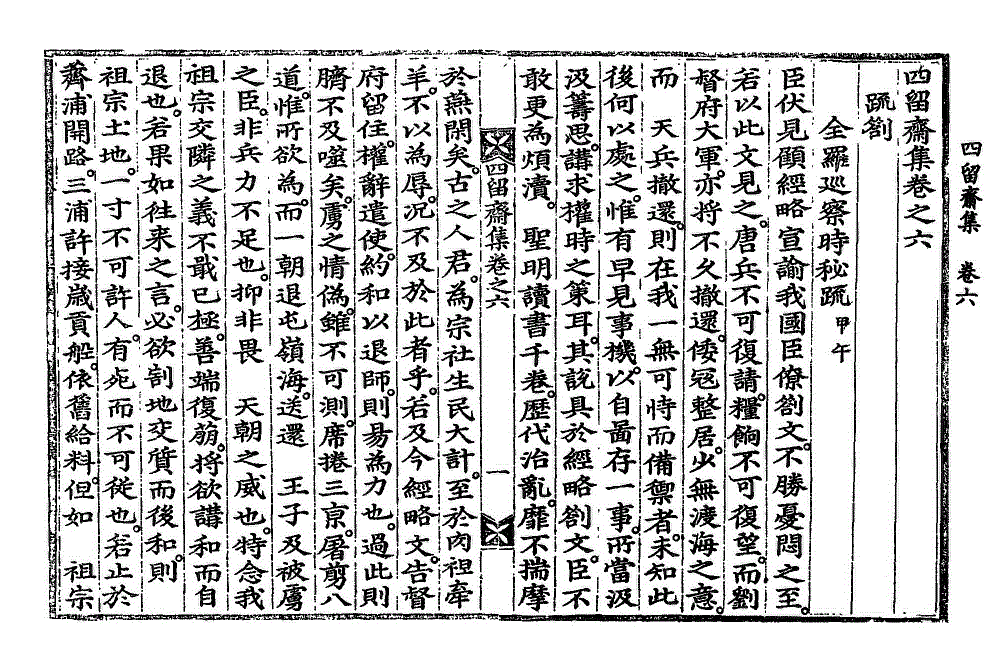 全罗巡察时秘疏(甲午)
全罗巡察时秘疏(甲午)臣伏见顾经略宣谕我国臣僚劄文。不胜忧闷之至。若以此文见之。唐兵不可复请。粮饷不可复望。而刘督府大军。亦将不久撤还。倭寇整居。少无渡海之意。而 天兵撤还。则在我一无可恃而备御者。未知此后何以处之。惟有早见事机。以自图存一事。所当汲汲筹思。讲求权时之策耳。其说具于经略劄文。臣不敢更为烦渎。 圣明读书千卷。历代治乱。靡不揣摩于燕闲矣。古之人君。为宗社生民大计。至于肉袒牵羊。不以为辱。况不及于此者乎。若及今经略文。告督府留住。权辞遣使。约和以退师。则易为力也。过此则脐不及噬矣。虏之情伪。虽不可测。席捲三京。屠剪八道。惟所欲为。而一朝退屯岭海。送还 王子及被虏之臣。非兵力不足也。抑非畏 天朝之威也。特念我祖宗交邻之义不戢已极。善端复萌。将欲讲和而自退也。若果如往来之言。必欲割地交质而后和。则 祖宗土地。一寸不可许人。有死而不可从也。若止于荠浦开路。三浦许接岁贡船。依旧给料。但如 祖宗
四留斋集卷之六 第 3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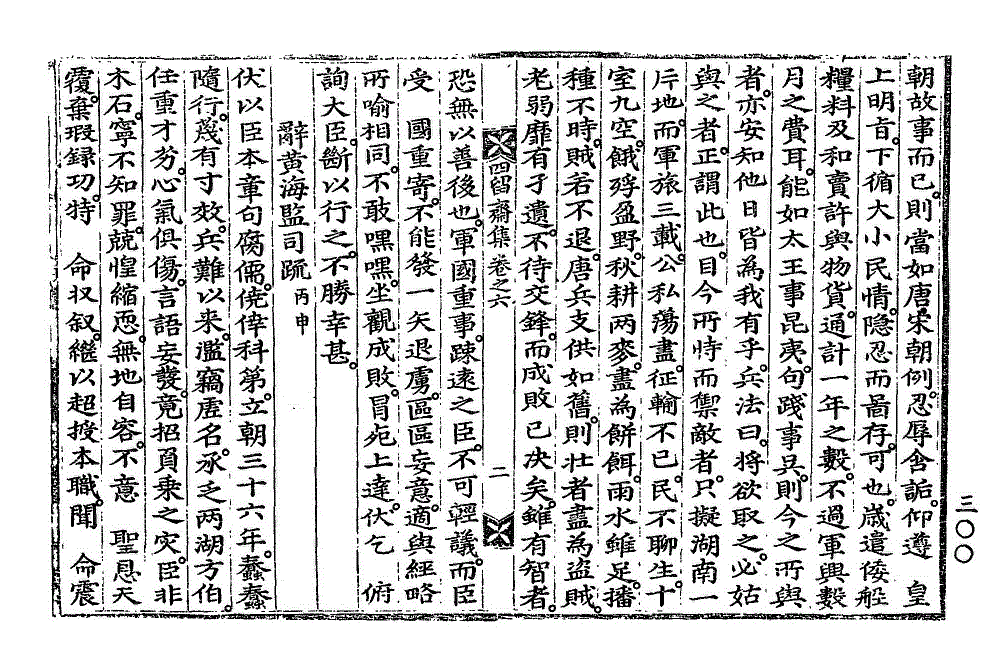 朝故事而已。则当如唐,宋朝例。忍辱含诟。仰遵 皇上明旨。下循大小民情。隐忍而啚存。可也。岁遣倭船粮料及和卖许与物货。通计一年之数。不过军兴数月之费耳。能如太王事昆夷。句践事吴。则今之所与者。亦安知他日皆为我有乎。兵法曰。将欲取之。必姑与之者。正谓此也。目今所恃而御敌者。只拟湖南一片地。而军旅三载。公私荡尽。征轮不已。民不聊生。十室九空。饿殍盈野。秋耕两麦。尽为饼饵。雨水虽足。播种不时。贼若不退。唐兵支供如旧。则壮者尽为盗贼。老弱靡有孑遗。不待交锋。而成败已决矣。虽有智者。恐无以善后也。军国重事。疏远之臣。不可轻议。而臣受 国重寄。不能发一矢退虏。区区妄意。适与经略所喻相同。不敢嘿嘿。坐观成败。冒死上达。伏乞 俯询大臣。断以行之。不胜幸甚。
朝故事而已。则当如唐,宋朝例。忍辱含诟。仰遵 皇上明旨。下循大小民情。隐忍而啚存。可也。岁遣倭船粮料及和卖许与物货。通计一年之数。不过军兴数月之费耳。能如太王事昆夷。句践事吴。则今之所与者。亦安知他日皆为我有乎。兵法曰。将欲取之。必姑与之者。正谓此也。目今所恃而御敌者。只拟湖南一片地。而军旅三载。公私荡尽。征轮不已。民不聊生。十室九空。饿殍盈野。秋耕两麦。尽为饼饵。雨水虽足。播种不时。贼若不退。唐兵支供如旧。则壮者尽为盗贼。老弱靡有孑遗。不待交锋。而成败已决矣。虽有智者。恐无以善后也。军国重事。疏远之臣。不可轻议。而臣受 国重寄。不能发一矢退虏。区区妄意。适与经略所喻相同。不敢嘿嘿。坐观成败。冒死上达。伏乞 俯询大臣。断以行之。不胜幸甚。辞黄海监司疏(丙申)
伏以臣本章句腐儒。侥倖科第。立朝三十六年。蠢蠢随行。蔑有寸效。兵难以来。滥窃虚名。承乏两湖方伯。任重才劣。心气俱伤。言语妄发。竟招负乘之灾。臣非木石。宁不知罪。兢惶缩恧。无地自容。不意 圣恩天覆。弃瑕录功。特 命收叙。继以超授本职。闻 命震
四留斋集卷之六 第 3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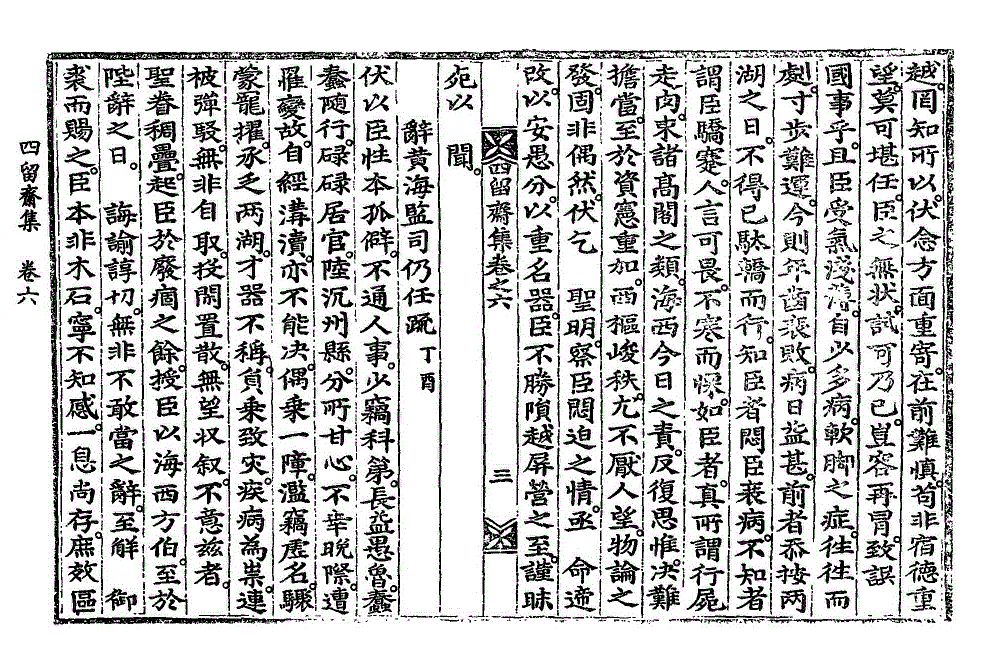 越。罔知所以。伏念方面重寄。在前难慎。苟非宿德重望。莫可堪任。臣之无状。试可乃已。岂容再冒。致误 国事乎。且臣受气浅薄。自少多病。软脚之症。往往而剧。寸步难运。今则年齿衰败。病日益甚。前者忝按两湖之日。不得已驮轿而行。知臣者闷臣衰病。不知者谓臣骄蹇。人言可畏。不寒而慄。如臣者。真所谓行尸走肉。束诸高阁之类。海西今日之责。反复思惟。决难担当。至于资宪重加。西枢峻秩。尤不厌人望。物论之发。固非偶然。伏乞 圣明。察臣闷迫之情。亟 命递改。以安愚分。以重名器。臣不胜陨越屏营之至。谨昧死以 闻。
越。罔知所以。伏念方面重寄。在前难慎。苟非宿德重望。莫可堪任。臣之无状。试可乃已。岂容再冒。致误 国事乎。且臣受气浅薄。自少多病。软脚之症。往往而剧。寸步难运。今则年齿衰败。病日益甚。前者忝按两湖之日。不得已驮轿而行。知臣者闷臣衰病。不知者谓臣骄蹇。人言可畏。不寒而慄。如臣者。真所谓行尸走肉。束诸高阁之类。海西今日之责。反复思惟。决难担当。至于资宪重加。西枢峻秩。尤不厌人望。物论之发。固非偶然。伏乞 圣明。察臣闷迫之情。亟 命递改。以安愚分。以重名器。臣不胜陨越屏营之至。谨昧死以 闻。辞黄海监司仍任疏(丁酉)
伏以臣性本孤僻。不通人事。少窃科第。长益愚鲁。蠢蠢随行。碌碌居官。陆沈州县。分所甘心。不幸晚际。遭罹变故。自经沟渎。亦不能决。偶乘一障。滥窃虚名。骤蒙宠擢。承乏两湖。才器不称。负乘致灾。疾病为祟。连被弹驳。无非自取。投闲置散。无望收叙。不意玆者。圣眷稠叠。起臣于废痼之馀。授臣以海西方伯。至于陛辞之日。 诲谕谆切。无非不敢当之辞。至解 御裘而赐之。臣本非木石。宁不知感。一息尚存。庶效区
四留斋集卷之六 第 3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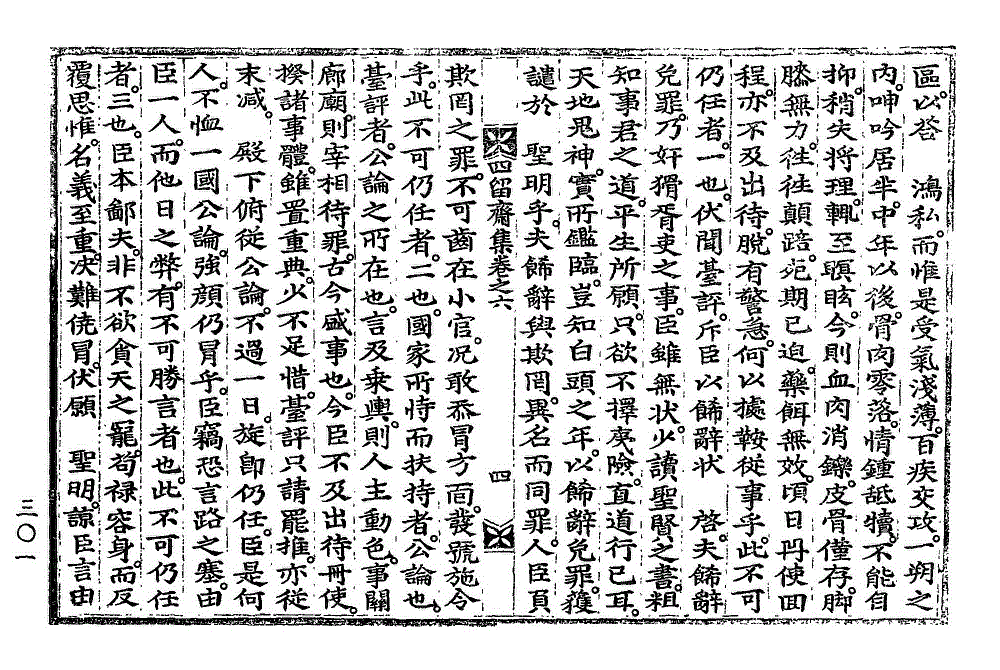 区。以答 鸿私。而惟是受气浅薄。百疾交攻。一朔之内。呻吟居半。中年以后。骨肉零落。情钟舐犊。不能自抑。稍失将理。辄至瞑眩。今则血肉消铄。皮骨仅存。脚膝无力。往往颠踣。死期已迫。药饵无效。顷日册使回程。亦不及出待。脱有警急。何以据鞍从事乎。此不可仍任者。一也。伏闻台评。斥臣以饰辞状 启。夫饰辞免罪。乃奸猾胥吏之事。臣虽无状。少读圣贤之书。粗知事君之道。平生所愿。只欲不择夷险。直道行已耳。天地鬼神。实所鉴临。岂知白头之年。以饰辞免罪。获谴于 圣明乎。夫饰辞与欺罔。异名而同罪。人臣负欺罔之罪。不可齿在小官。况敢忝冒方面。发号施令乎。此不可仍任者。二也。国家所恃而扶持者。公论也。台评者。公论之所在也。言及乘舆。则人主动色。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古今盛事也。今臣不及出待册使。揆诸事体。虽置重典。少不足惜。台评只请罢推。亦从末减。 殿下俯从公论。不过一日。旋即仍任。臣是何人。不恤一国公论。强颜仍冒乎。臣窃恐言路之塞。由臣一人。而他日之弊。有不可胜言者也。此不可仍任者。三也。臣本鄙夫。非不欲贪天之宠。苟禄容身。而反覆思惟。名义至重。决难侥冒。伏愿 圣明。谅臣言由
区。以答 鸿私。而惟是受气浅薄。百疾交攻。一朔之内。呻吟居半。中年以后。骨肉零落。情钟舐犊。不能自抑。稍失将理。辄至瞑眩。今则血肉消铄。皮骨仅存。脚膝无力。往往颠踣。死期已迫。药饵无效。顷日册使回程。亦不及出待。脱有警急。何以据鞍从事乎。此不可仍任者。一也。伏闻台评。斥臣以饰辞状 启。夫饰辞免罪。乃奸猾胥吏之事。臣虽无状。少读圣贤之书。粗知事君之道。平生所愿。只欲不择夷险。直道行已耳。天地鬼神。实所鉴临。岂知白头之年。以饰辞免罪。获谴于 圣明乎。夫饰辞与欺罔。异名而同罪。人臣负欺罔之罪。不可齿在小官。况敢忝冒方面。发号施令乎。此不可仍任者。二也。国家所恃而扶持者。公论也。台评者。公论之所在也。言及乘舆。则人主动色。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古今盛事也。今臣不及出待册使。揆诸事体。虽置重典。少不足惜。台评只请罢推。亦从末减。 殿下俯从公论。不过一日。旋即仍任。臣是何人。不恤一国公论。强颜仍冒乎。臣窃恐言路之塞。由臣一人。而他日之弊。有不可胜言者也。此不可仍任者。三也。臣本鄙夫。非不欲贪天之宠。苟禄容身。而反覆思惟。名义至重。决难侥冒。伏愿 圣明。谅臣言由四留斋集卷之六 第 3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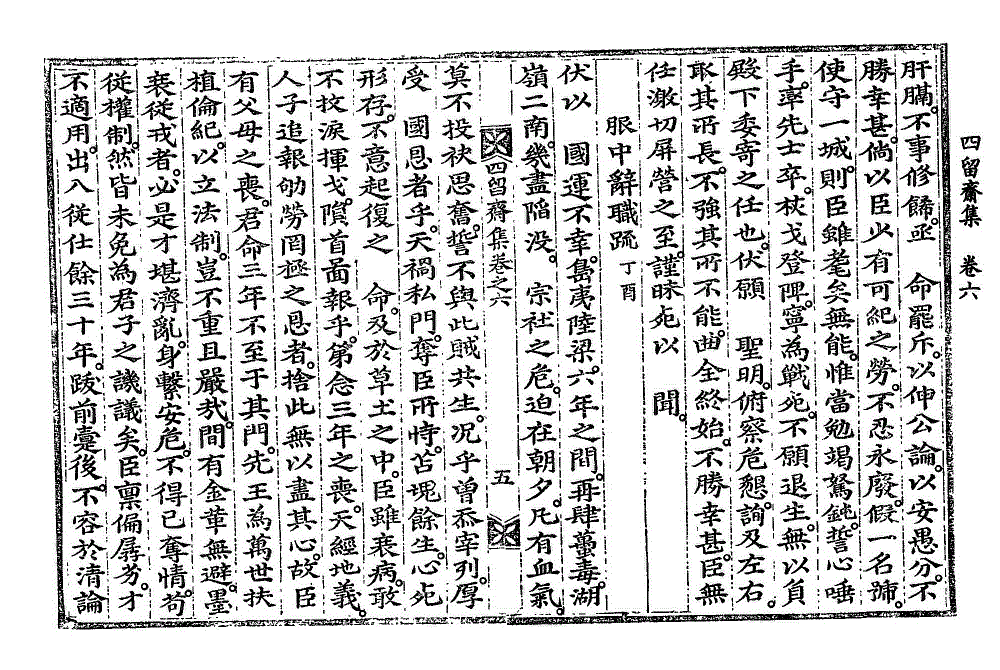 肝膈。不事修饰。亟 命罢斥。以伸公论。以安愚分。不胜幸甚。倘以臣少有可纪之劳。不忍永废。假一名号。使守一城。则臣虽耄矣无能。惟当勉竭驽钝。誓心唾手。率先士卒。杖戈登陴。宁为战死。不愿退生。无以负殿下委寄之任也。伏愿 圣明。俯察危恳。询及左右。取其所长。不强其所不能。曲全终始。不胜幸甚。臣无任激切屏营之至。谨昧死以 闻。
肝膈。不事修饰。亟 命罢斥。以伸公论。以安愚分。不胜幸甚。倘以臣少有可纪之劳。不忍永废。假一名号。使守一城。则臣虽耄矣无能。惟当勉竭驽钝。誓心唾手。率先士卒。杖戈登陴。宁为战死。不愿退生。无以负殿下委寄之任也。伏愿 圣明。俯察危恳。询及左右。取其所长。不强其所不能。曲全终始。不胜幸甚。臣无任激切屏营之至。谨昧死以 闻。服中辞职疏(丁酉)
伏以 国运不幸。岛夷陆梁。六年之间。再肆虿毒。湖岭二南。几尽陷没。 宗社之危。迫在朝夕。凡有血气。莫不投袂思奋。誓不与此贼共生。况乎曾忝宰列。厚受国 恩者乎。天祸私门。夺臣所恃。苫块馀生。心死形存。不意起复之 命。及于草土之中。臣虽衰病。敢不抆泪挥戈。陨首啚报乎。第念三年之丧。天经地义。人子追报劬劳罔极之恩者。舍此无以尽其心。故臣有父母之丧。君命三年不至于其门。先王为万世扶植伦纪。以立法制。岂不重且严哉。间有金革无避。墨衰从戎者。必是才堪济乱。身系安危。不得已夺情。苟从权制。然皆未免为君子之讥议矣。臣禀偏孱劣。才不适用。出入从仕馀三十年。跋前疐后。不容于清论
四留斋集卷之六 第 3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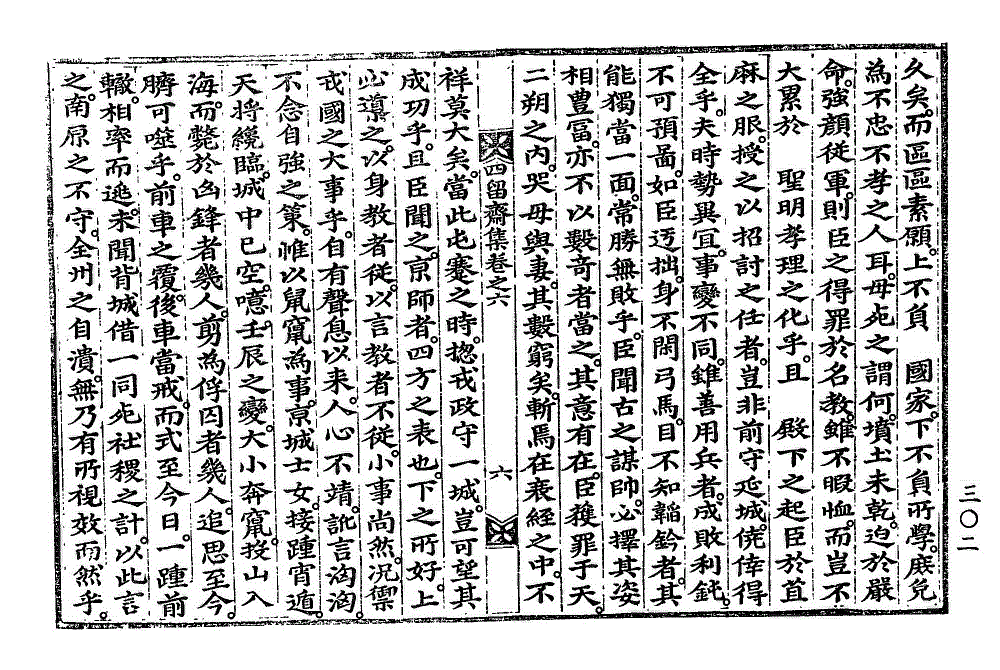 久矣。而区区素愿。上不负 国家。下不负所学。庶免为不忠不孝之人耳。毋死之谓何。坟土未乾。迫于严命。强颜从军。则臣之得罪于名教。虽不暇恤。而岂不大累于 圣明孝理之化乎。且 殿下之起臣于苴麻之服。授之以招讨之任者。岂非前守延城。侥倖得全乎。夫时势异宜。事变不同。虽善用兵者。成败利钝。不可预啚。如臣迂拙。身不闲弓马。目不知韬钤者。其能独当一面。常胜无败乎。臣闻古之谋帅。必择其姿相丰富。亦不以数奇者当之。其意有在。臣获罪于天。二朔之内。哭母与妻。其数穷矣。斩马在衰绖之中。不祥莫大矣。当此屯蹇之时。总戎政守一城。岂可望其成功乎。且臣闻之。京师者。四方之表也。下之所好。上必导之。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不从。小事尚然。况御戎国之大事乎。自有声息以来。人心不靖。讹言汹汹。不念自强之策。惟以鼠窜为事。京城士女。接踵宵遁。天将才临。城中已空。噫。壬辰之变。大小奔窜。投山入海。而毙于凶锋者几人。剪为俘囚者几人。追思至今。脐可噬乎。前车之覆。后车当戒。而式至今日。一踵前辙。相率而逃。未闻背城借一同死社稷之计。以此言之。南原之不守。全州之自溃。无乃有所视效而然乎。
久矣。而区区素愿。上不负 国家。下不负所学。庶免为不忠不孝之人耳。毋死之谓何。坟土未乾。迫于严命。强颜从军。则臣之得罪于名教。虽不暇恤。而岂不大累于 圣明孝理之化乎。且 殿下之起臣于苴麻之服。授之以招讨之任者。岂非前守延城。侥倖得全乎。夫时势异宜。事变不同。虽善用兵者。成败利钝。不可预啚。如臣迂拙。身不闲弓马。目不知韬钤者。其能独当一面。常胜无败乎。臣闻古之谋帅。必择其姿相丰富。亦不以数奇者当之。其意有在。臣获罪于天。二朔之内。哭母与妻。其数穷矣。斩马在衰绖之中。不祥莫大矣。当此屯蹇之时。总戎政守一城。岂可望其成功乎。且臣闻之。京师者。四方之表也。下之所好。上必导之。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不从。小事尚然。况御戎国之大事乎。自有声息以来。人心不靖。讹言汹汹。不念自强之策。惟以鼠窜为事。京城士女。接踵宵遁。天将才临。城中已空。噫。壬辰之变。大小奔窜。投山入海。而毙于凶锋者几人。剪为俘囚者几人。追思至今。脐可噬乎。前车之覆。后车当戒。而式至今日。一踵前辙。相率而逃。未闻背城借一同死社稷之计。以此言之。南原之不守。全州之自溃。无乃有所视效而然乎。四留斋集卷之六 第 303H 页
 大福不再。愚民难牖。海州山城。宁保其必守乎。臣生逢离乱。常痛不知死所。今虽不幸死于首阳山中。得与二子同游地下。死亦荣矣。未知 殿下一出都门。人心溃散。则毕竟税驾于何地。思之至此。不觉抚膺痛哭也。伏愿 圣明怜臣重服在身。谅臣疾病缠骨。亟收 成命。俾从中制。则臣生虽无益于成败。死当结草而抗贼也。哀疚之中。精神荒迷。言不知裁。伏愿圣明矜察焉。不胜悲哀闷迫之至。谨昧死以 闻。
大福不再。愚民难牖。海州山城。宁保其必守乎。臣生逢离乱。常痛不知死所。今虽不幸死于首阳山中。得与二子同游地下。死亦荣矣。未知 殿下一出都门。人心溃散。则毕竟税驾于何地。思之至此。不觉抚膺痛哭也。伏愿 圣明怜臣重服在身。谅臣疾病缠骨。亟收 成命。俾从中制。则臣生虽无益于成败。死当结草而抗贼也。哀疚之中。精神荒迷。言不知裁。伏愿圣明矜察焉。不胜悲哀闷迫之至。谨昧死以 闻。辞招讨使疏(丁酉)
伏以守城第一急务。不过足兵足食而已。目今岛夷席捲两湖。退还窟穴。非其兵力不足。欲为分兵肆楚之计。今年攻陷某道。明年攻陷某道。至于皮尽毛无所付而后已。万一 天兵。以刍粮不继而旋归。则来年贼锋。未知向于何道。以臣愚计。其祸必及于延城。何者。延城在西路初程。而壬辰之变。虏尝不得逞志。狺然凶狡之心。必欲吞噬而后甘心焉。其设心如是。则其攻击之谋。必不如前日之轻举也。 朝廷若以延城成败。不关于国之存亡。则当预为之所。不可使孑遗之民。为鱼为肉而莫之恤也。若以一邑一城。皆先王世守之地。不可弃焉。则所当十分区画。积谷鍊
四留斋集卷之六 第 3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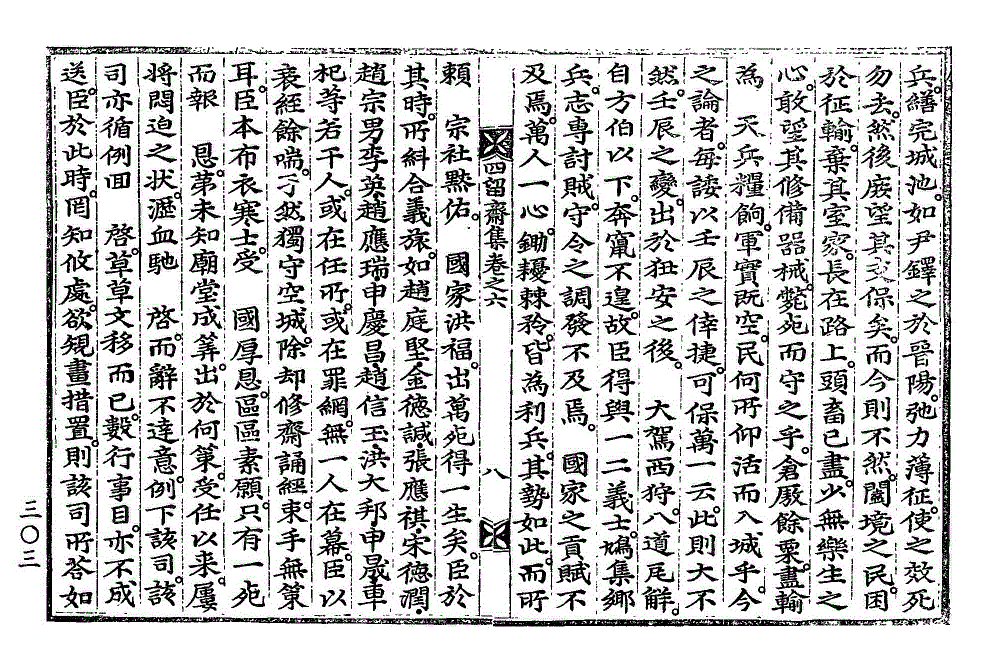 兵。缮完城池。如尹铎之于晋阳。弛力簿征。使之效死勿去。然后庶望其支保矣。而今则不然。阖境之民。困于征输。弃其室家。长在路上。头畜已尽。少无乐生之心。敢望其修备器械。毙死而守之乎。仓廒馀粟。尽输为 天兵粮饷。军实既空。民何所仰活而入城乎。今之论者。每诿以壬辰之倖捷。可保万一云。此则大不然。壬辰之变。出于狃安之后。 大驾西狩。八道瓦解。自方伯以下。奔窜不遑。故臣得与一二义士。鸠集乡兵。志专讨贼。守令之调发不及焉。 国家之贡赋不及焉。万人一心。锄耰棘矜。皆为利兵。其势如此。而所赖宗社默佑。 国家洪福。出万死得一生矣。臣于其时。所紏合义旅。如赵庭坚,金德諴,张应帺,宋德润,赵宗男,李英,赵应瑞,申庆昌,赵信玉,洪大邦,申晟,车杞等若干人。或在任所。或在罪网。无一人在幕。臣以衰绖馀喘。孑然独守空城。除却修斋诵经。束手无策耳。臣本布衣寒士。受 国厚恩。区区素愿。只有一死而报 恩。第未知庙堂成算。出于何策。受任以来。屡将闷迫之状。沥血驰 启。而辞不达意。例下该司。该司亦循例回 启。草草文移而已。数行事目。亦不成送。臣于此时。罔知攸处。欲规画措置。则该司所答如
兵。缮完城池。如尹铎之于晋阳。弛力簿征。使之效死勿去。然后庶望其支保矣。而今则不然。阖境之民。困于征输。弃其室家。长在路上。头畜已尽。少无乐生之心。敢望其修备器械。毙死而守之乎。仓廒馀粟。尽输为 天兵粮饷。军实既空。民何所仰活而入城乎。今之论者。每诿以壬辰之倖捷。可保万一云。此则大不然。壬辰之变。出于狃安之后。 大驾西狩。八道瓦解。自方伯以下。奔窜不遑。故臣得与一二义士。鸠集乡兵。志专讨贼。守令之调发不及焉。 国家之贡赋不及焉。万人一心。锄耰棘矜。皆为利兵。其势如此。而所赖宗社默佑。 国家洪福。出万死得一生矣。臣于其时。所紏合义旅。如赵庭坚,金德諴,张应帺,宋德润,赵宗男,李英,赵应瑞,申庆昌,赵信玉,洪大邦,申晟,车杞等若干人。或在任所。或在罪网。无一人在幕。臣以衰绖馀喘。孑然独守空城。除却修斋诵经。束手无策耳。臣本布衣寒士。受 国厚恩。区区素愿。只有一死而报 恩。第未知庙堂成算。出于何策。受任以来。屡将闷迫之状。沥血驰 启。而辞不达意。例下该司。该司亦循例回 启。草草文移而已。数行事目。亦不成送。臣于此时。罔知攸处。欲规画措置。则该司所答如四留斋集卷之六 第 3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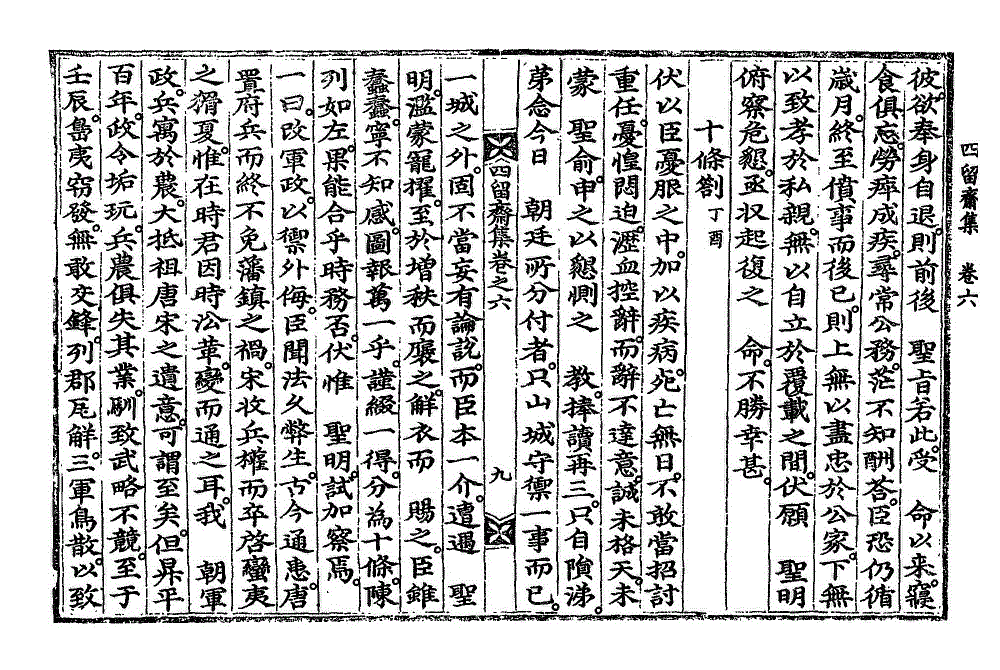 彼。欲奉身自退。则前后 圣旨若此。受 命以来。寝食俱忘。劳瘁成疾。寻常公务。茫不知酬答。臣恐仍循岁月。终至偾事而后已。则上无以尽忠于公家。下无以致孝于私亲。无以自立于覆载之间。伏愿 圣明俯察危恳。亟收起复之 命。不胜幸甚。
彼。欲奉身自退。则前后 圣旨若此。受 命以来。寝食俱忘。劳瘁成疾。寻常公务。茫不知酬答。臣恐仍循岁月。终至偾事而后已。则上无以尽忠于公家。下无以致孝于私亲。无以自立于覆载之间。伏愿 圣明俯察危恳。亟收起复之 命。不胜幸甚。十条劄(丁酉)
伏以臣忧服之中。加以疾病。死亡无日。不敢当招讨重任。忧惶闷迫。沥血控辞。而辞不达意。诚未格天。未蒙 圣俞。申之以恳恻之 教。捧读再三。只自陨涕。第念今日 朝廷所分付者。只山城守御一事而已。一城之外。固不当妄有论说。而臣本一介。遭遇 圣明。滥蒙宠擢。至于增秩而褒之。解衣而 赐之。臣虽蠢蠢。宁不知感。图报万一乎。谨缀一得。分为十条。陈列如左。果能合乎时务否。伏惟 圣明。试加察焉。一曰。改军政。以御外侮。臣闻法久弊生。古今通患。唐置府兵而终不免藩镇之祸。宋收兵权而卒启蛮夷之猾夏。惟在时君因时沿革。变而通之耳。我 朝军政。兵寓于农。大抵祖唐宋之遗意。可谓至矣。但升乎百年。政令垢玩。兵农俱失其业。驯致武略不竞。至于壬辰。岛夷窃发。无敢交锋。列郡瓦解。三军鸟散。以致
四留斋集卷之六 第 3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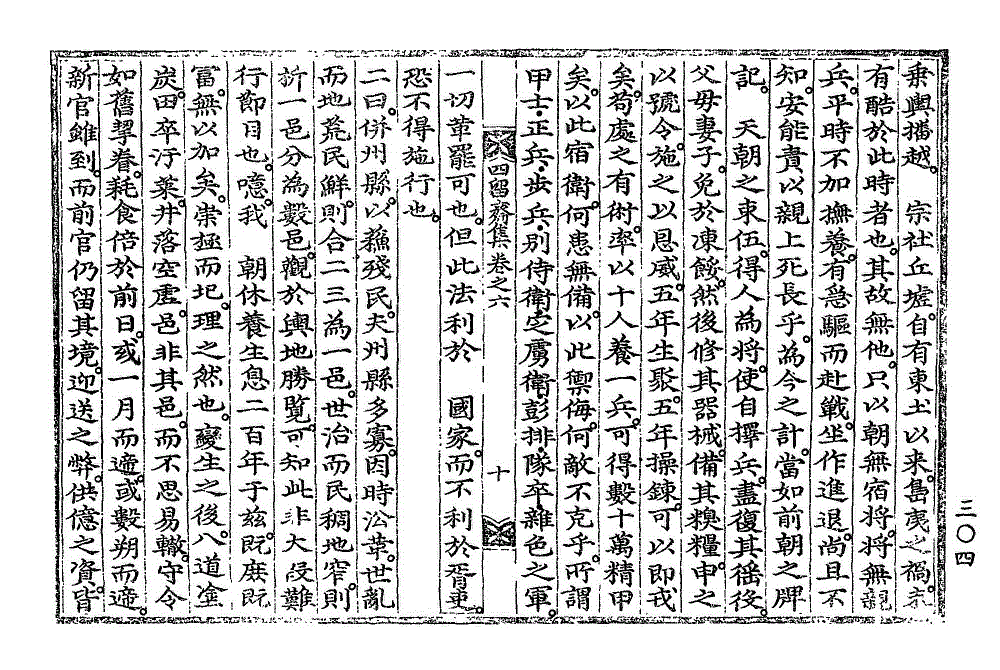 乘舆播越。 宗社兵墟。自有东土以来。岛夷之祸。未有酷于此时者也。其故无他。只以朝无宿将。将无亲兵。平时不加抚养。有急驱而赴战。坐作进退。尚且不知。安能责以亲上死长乎。为今之计。当如前朝之牌记。 天朝之束伍。得人为将。使自择兵。尽复其徭役。父母妻子。免于冻馁。然后修其器械。备其糗粮。申之以号令。施之以恩威。五年生聚。五年操鍊。可以即戎矣。苟处之有术。率以十人养一兵。可得数十万精甲矣。以此宿卫。何患无备。以此御侮。何敌不克乎。所谓甲士,正兵,步兵,别侍卫,定虏卫,彭排,队卒,杂色之军。一切革罢可也。但此法利于 国家。而不利于胥吏。恐不得施行也。
乘舆播越。 宗社兵墟。自有东土以来。岛夷之祸。未有酷于此时者也。其故无他。只以朝无宿将。将无亲兵。平时不加抚养。有急驱而赴战。坐作进退。尚且不知。安能责以亲上死长乎。为今之计。当如前朝之牌记。 天朝之束伍。得人为将。使自择兵。尽复其徭役。父母妻子。免于冻馁。然后修其器械。备其糗粮。申之以号令。施之以恩威。五年生聚。五年操鍊。可以即戎矣。苟处之有术。率以十人养一兵。可得数十万精甲矣。以此宿卫。何患无备。以此御侮。何敌不克乎。所谓甲士,正兵,步兵,别侍卫,定虏卫,彭排,队卒,杂色之军。一切革罢可也。但此法利于 国家。而不利于胥吏。恐不得施行也。二曰。并州县。以苏残民。夫州县多寡。因时沿革。世乱而地荒民鲜。则合二三为一邑。世治而民稠地窄。则析一邑分为数邑。观于舆地胜览。可知此非大段难行节目也。噫。我 朝休养生息二百年于玆。既庶既富。无以加矣。崇极而圮。理之然也。变生之后。八道涂炭。田卒污莱。井落空虚。邑非其邑。而不思易辙。守令如旧挈眷。耗食倍于前日。或一月而遆。或数朔而遆。新官虽到。而前官仍留其境。迎送之弊。供亿之资。皆
四留斋集卷之六 第 3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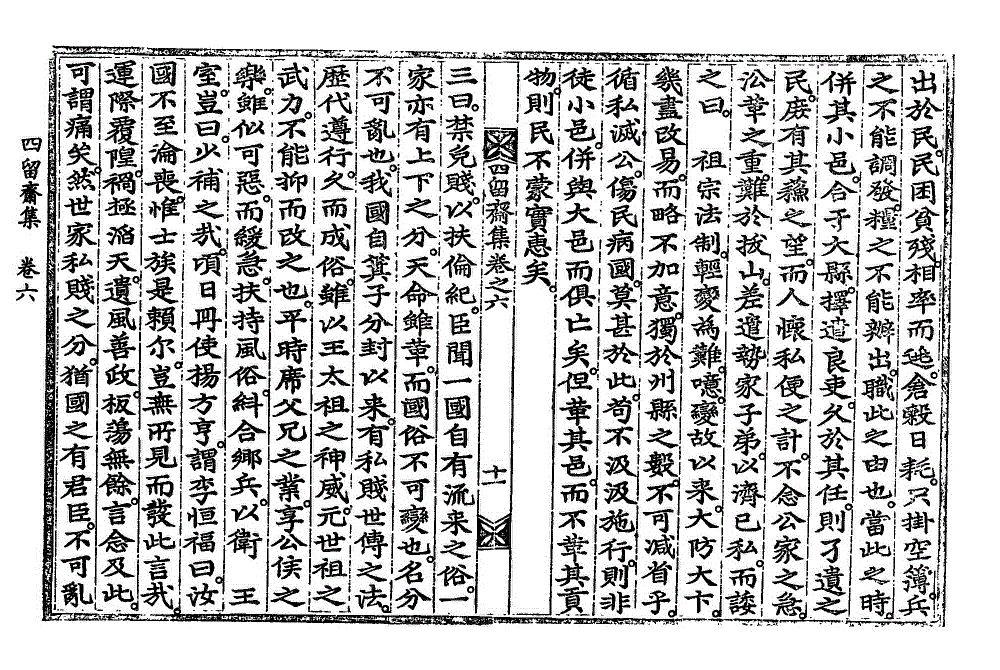 出于民。民困贫残。相率而逃。仓谷日耗。只挂空簿。兵之不能调发。粮之不能办出。职此之由也。当此之时。并其小邑。合于大县。择遣良吏。久于其任。则孑遗之民。庶有其苏之望。而人怀私便之计。不念公家之急。沿革之重。难于拔山。差遣势家子弟。以济已私。而诿之曰。 祖宗法制。轻变为难。噫。变故以来。大防大卞。几尽改易。而略不加意。独于州县之数。不可减省乎。循私灭公。伤民病国。莫甚于此。苟不汲汲施行。则非徒小邑。并与大邑而俱亡矣。但革其邑。而不革其贡物。则民不蒙实惠矣。
出于民。民困贫残。相率而逃。仓谷日耗。只挂空簿。兵之不能调发。粮之不能办出。职此之由也。当此之时。并其小邑。合于大县。择遣良吏。久于其任。则孑遗之民。庶有其苏之望。而人怀私便之计。不念公家之急。沿革之重。难于拔山。差遣势家子弟。以济已私。而诿之曰。 祖宗法制。轻变为难。噫。变故以来。大防大卞。几尽改易。而略不加意。独于州县之数。不可减省乎。循私灭公。伤民病国。莫甚于此。苟不汲汲施行。则非徒小邑。并与大邑而俱亡矣。但革其邑。而不革其贡物。则民不蒙实惠矣。三曰。禁免贱。以扶伦纪。臣闻一国自有流来之俗。一家亦有上下之分。天命虽革。而国俗不可变也。名分不可乱也。我国自箕子分封以来。有私贱世传之法。历代遵行。久而成俗。虽以王太祖之神威。元世祖之武力。不能抑而改之也。平时席父兄之业。享公侯之乐。虽似可恶。而缓急。扶持风俗。紏合乡兵。以卫 王室。岂曰。少补之哉。项日册使杨方亨。谓李恒福曰。汝国不至沦丧。惟士族是赖尔。岂无所见而发此言哉。运际覆隍。祸极滔天。遗风善政。板荡无馀。言念及此。可谓痛哭。然世家私贱之分。犹国之有君臣。不可乱
四留斋集卷之六 第 3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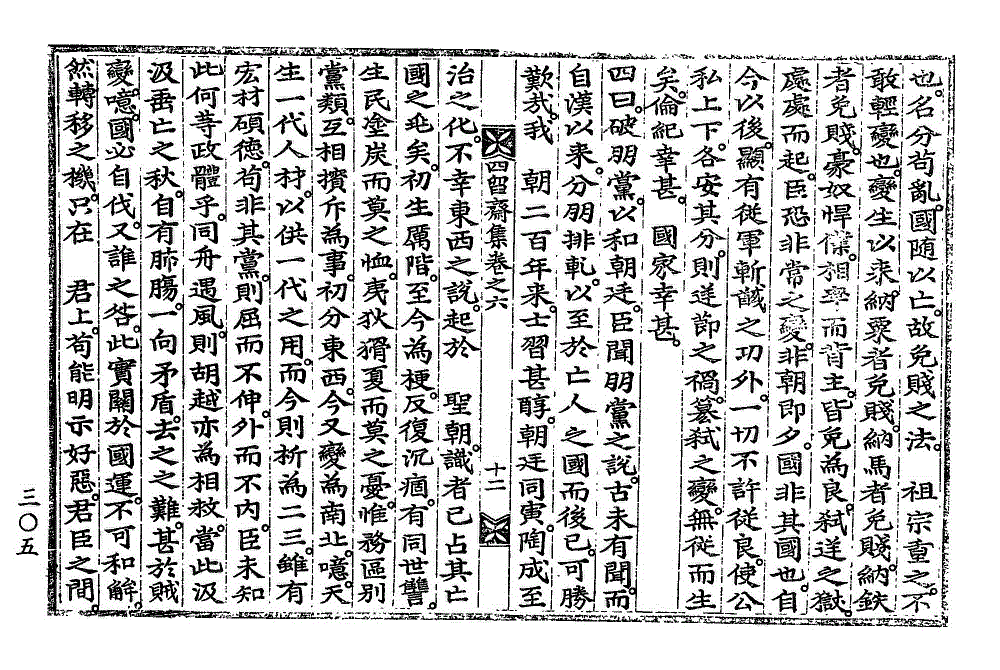 也。名分苟乱。国随以亡。故免贱之法。 祖宗重之。不敢轻变也。变生以来。纳粟者免贱。纳马者免贱。纳铁者免贱。豪奴悍仆。相率而背主。皆免为良。弑逆之狱。处处而起。臣恐非常之变。非朝即夕。国非其国也。自今以后。显有从军斩馘之功外。一切不许从良。使公私上下。各安其分。则逆节之祸。篡弑之变。无从而生矣。伦纪幸甚。 国家幸甚。
也。名分苟乱。国随以亡。故免贱之法。 祖宗重之。不敢轻变也。变生以来。纳粟者免贱。纳马者免贱。纳铁者免贱。豪奴悍仆。相率而背主。皆免为良。弑逆之狱。处处而起。臣恐非常之变。非朝即夕。国非其国也。自今以后。显有从军斩馘之功外。一切不许从良。使公私上下。各安其分。则逆节之祸。篡弑之变。无从而生矣。伦纪幸甚。 国家幸甚。四曰。破朋党。以和朝廷。臣闻朋党之说。古来有闻。而自汉以来。分朋排轧。以至于亡人之国而后已。可胜叹哉。我 朝二百年来。士习甚醇。朝廷同寅。陶成至治之化。不幸东西之说。起于 圣朝。识者已占其亡国之兆矣。初生厉阶。至今为梗。反复沈痼。有同世雠。生民涂炭而莫之恤。夷狄猾夏而莫之忧。惟务区别党类。互相摈斥为事。初分东西。今又变为南北。噫。天生一代人材。以供一代之用。而今则析为二三。虽有宏材硕德。苟非其党。则屈而不伸。外而不内。臣未知此何等政体乎。同舟遇风。则胡越亦为相救。当此汲汲垂亡之秋。自有肺肠。一向矛盾。去之之难。甚于贼变。噫。国必自伐。又谁之咎。此实关于国运。不可和解。然转移之机。只在 君上。苟能明示好恶。君臣之间。
四留斋集卷之六 第 3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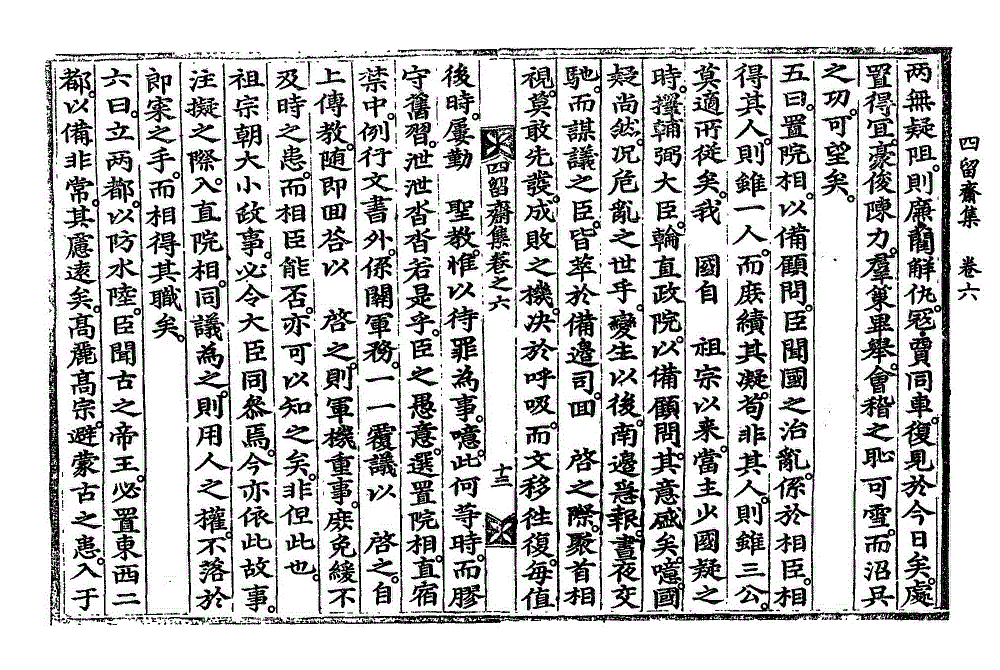 两无疑阻。则廉,蔺解仇。寇,贾同车。复见于今日矣。处置得宜。豪俊陈力。群策毕举。会稽之耻可雪。而沼吴之功。可望矣。
两无疑阻。则廉,蔺解仇。寇,贾同车。复见于今日矣。处置得宜。豪俊陈力。群策毕举。会稽之耻可雪。而沼吴之功。可望矣。五曰。置院相。以备顾问。臣闻国之治乱。系于相臣。相得其人。则虽一人。而庶绩其凝。苟非其人。则虽三公。莫适所从矣。我 国自 祖宗以来。当主少国疑之时。择辅弼大臣。轮直政院。以备顾问。其意盛矣。噫。国疑尚然。况危乱之世乎。变生以后。南边急报。昼夜交驰。而谋议之臣。皆萃于备边司。回 启之际。聚首相视。莫敢先发。成败之机。决于呼吸。而文移往复。每值后时。屡勤 圣教。惟以待罪为事。噫。此何等时。而胶守旧习。泄泄沓沓若是乎。臣之愚意。选置院相。直宿禁中。例行文书外。系关军务。一一覆议以 启之。自上传教。随即回答以 启之。则军机重事。庶免缓不及时之患。而相臣能否。亦可以知之矣。非但此也。 祖宗朝大小政事。必令大臣同参焉。今亦依此故事。注拟之际。入直院相。同议为之。则用人之权。不落于郎采之手。而相得其职矣。
六曰。立两都。以防水陆。臣闻古之帝王。必置东西二都。以备非常。其虑远矣。高丽高宗。避蒙古之患。入于
四留斋集卷之六 第 3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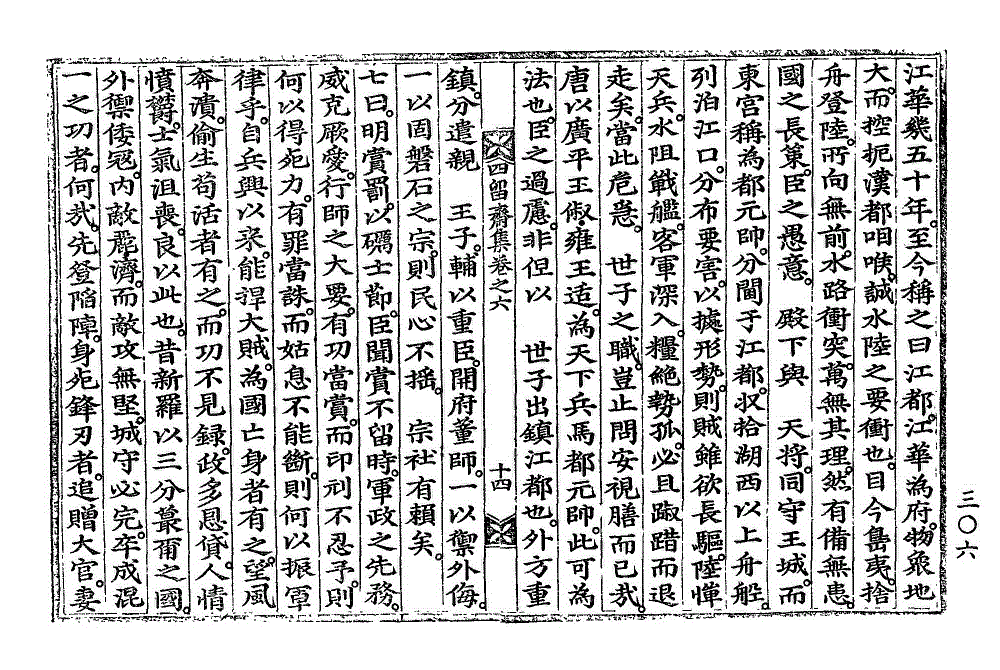 江华几五十年。至今称之曰江都。江华为府。物众地大。而控扼汉都咽喉。诚水陆之要冲也。目今岛夷。舍舟登陆。所向无前。水路冲突。万无其理。然有备无患。国之长策。臣之愚意。 殿下与 天将。固守王城。而东宫称为都元帅。分阃于江都。收拾湖西以上舟船。列泊江口。分布要害。以据形势。则贼虽欲长驱。陆惮天兵。水阻战舰。客军深入。粮绝势孤。必且踧踖而退走矣。当此危急。 世子之职。岂止问安视膳而已哉。唐以广平王俶,雍王适。为天下兵马都元帅。此可为法也。臣之过虑。非但以 世子出镇江都也。外方重镇。分遣亲 王子。辅以重臣。开府蕫师。一以御外侮。一以固磐石之宗。则民心不摇。 宗社有赖矣。
江华几五十年。至今称之曰江都。江华为府。物众地大。而控扼汉都咽喉。诚水陆之要冲也。目今岛夷。舍舟登陆。所向无前。水路冲突。万无其理。然有备无患。国之长策。臣之愚意。 殿下与 天将。固守王城。而东宫称为都元帅。分阃于江都。收拾湖西以上舟船。列泊江口。分布要害。以据形势。则贼虽欲长驱。陆惮天兵。水阻战舰。客军深入。粮绝势孤。必且踧踖而退走矣。当此危急。 世子之职。岂止问安视膳而已哉。唐以广平王俶,雍王适。为天下兵马都元帅。此可为法也。臣之过虑。非但以 世子出镇江都也。外方重镇。分遣亲 王子。辅以重臣。开府蕫师。一以御外侮。一以固磐石之宗。则民心不摇。 宗社有赖矣。七曰。明赏罚以砺士节。臣闻赏不留时。军政之先务。威克厥爱。行师之大要。有功当赏。而印刓不忍予。则何以得死力。有罪当诛。而姑息不能断。则何以振军律乎。自兵兴以来。能捍大贼。为国亡身者有之。望风奔溃。偷生苟活者有之。而功不见录。政多恩贷。人情愤郁。士气沮丧。良以此也。昔新罗以三分蕞尔之国。外御倭寇。内敌丽,济。而敌攻无坚。城守必完。卒成混一之功者。何哉。先登陷阵。身死锋刃者。追赠大官。妻
四留斋集卷之六 第 3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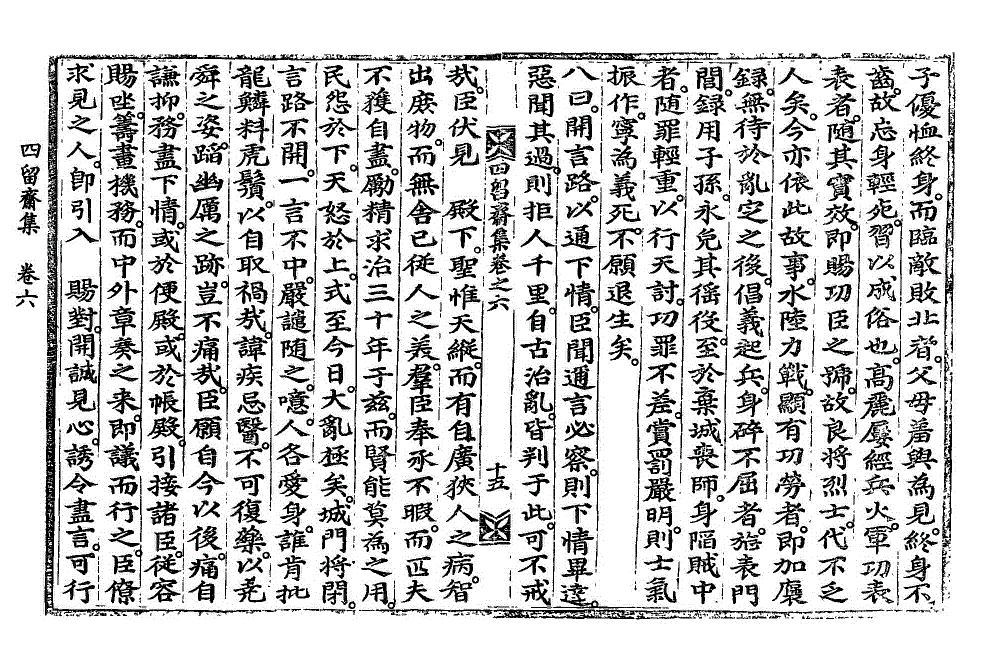 子优恤终身。而临敌败北者。父母羞与为见。终身不齿。故忘身轻死。习以成俗也。高丽屡经兵火。军功表表者。随其实效。即赐功臣之号。故良将烈士。代不乏人矣。今亦依此故事。水陆力战。显有功劳者。即加褒录。无待于乱定之后。倡义起兵。身碎不屈者。旌表门闾。录用子孙。永免其徭役。至于弃城丧帅。身陷贼中者。随罪轻重。以行天讨。功罪不差。赏罚严明。则士气振作。宁为义死。不愿退生矣。
子优恤终身。而临敌败北者。父母羞与为见。终身不齿。故忘身轻死。习以成俗也。高丽屡经兵火。军功表表者。随其实效。即赐功臣之号。故良将烈士。代不乏人矣。今亦依此故事。水陆力战。显有功劳者。即加褒录。无待于乱定之后。倡义起兵。身碎不屈者。旌表门闾。录用子孙。永免其徭役。至于弃城丧帅。身陷贼中者。随罪轻重。以行天讨。功罪不差。赏罚严明。则士气振作。宁为义死。不愿退生矣。八曰。开言路。以通下情。臣闻迩言必察。则下情毕达。恶闻其过。则拒人千里。自古治乱。皆判于此。可不戒哉。臣伏见 殿下。圣惟天纵。而有自广狭人之病。智出庶物。而无舍已从人之美。群臣奉承不暇。而匹夫不获自尽。励精求治三十年于玆。而贤能莫为之用。民怨于下。天怒于上。式至今日。大乱极矣。城门将闭。言路不开。一言不中。严谴随之。噫。人各爱身。谁肯批龙鳞料虎须。以自取祸哉。讳疾忌医。不可复药。以尧舜之姿。蹈幽厉之迹。岂不痛哉。臣愿自今以后。痛自谦抑。务尽下情。或于便殿。或于帐殿。引接诸臣。从容赐坐。筹画机务。而中外章奏之来。即议而行之。臣僚求见之人。即引入 赐对。开诚见心。诱令尽言。可行
四留斋集卷之六 第 3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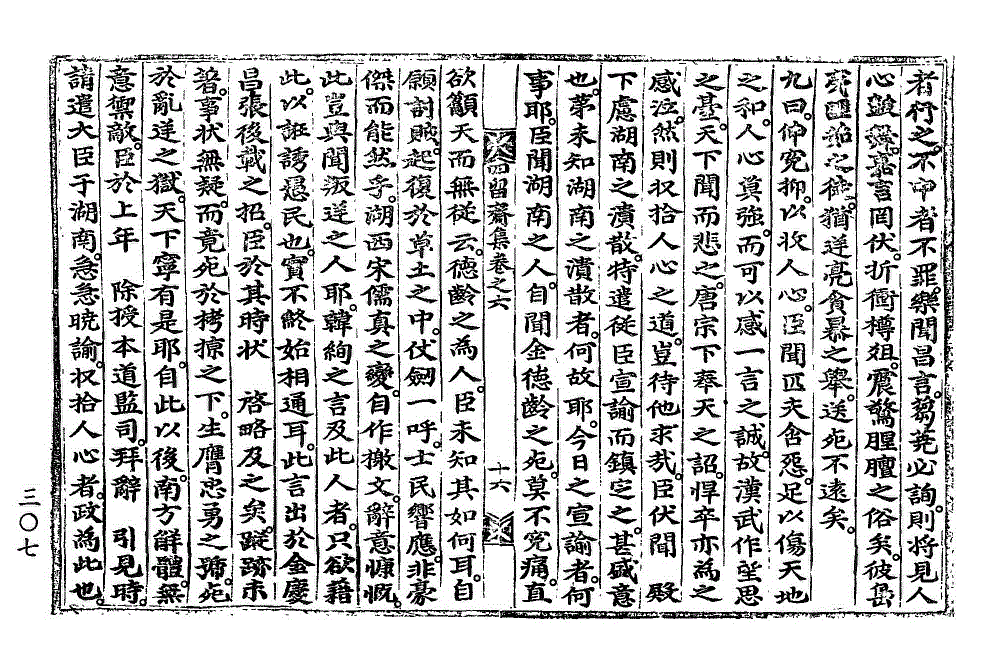 者行之。不中者不罪。乐闻昌言。刍荛必询。则将见人心鼓舞。嘉言罔伏。折冲樽俎。震惊腥膻之俗矣。彼岛夷匪茹之徒。犹逆亮贪暴之举。送死不远矣。
者行之。不中者不罪。乐闻昌言。刍荛必询。则将见人心鼓舞。嘉言罔伏。折冲樽俎。震惊腥膻之俗矣。彼岛夷匪茹之徒。犹逆亮贪暴之举。送死不远矣。九曰。伸冤抑。以收人心。臣闻匹夫含怨。足以伤天地之和。人心莫强。而可以感一言之诚。故汉武作望思之台。天下闻而悲之。唐宗下奉天之诏。悍卒亦为之感泣。然则收拾人心之道。岂待他求哉。臣伏闻 殿下虑湖南之溃散。特遣从臣宣谕而镇定之。甚盛意也。第未知湖南之溃散者。何故耶。今日之宣谕者。何事耶。臣闻湖南之人。自闻金德龄之死。莫不冤痛。直欲吁天而无从云。德龄之为人。臣未知其如何耳。自愿讨贼。起复于草土之中。仗剑一呼。士民响应。非豪杰而能然乎。湖西宋儒真之变。自作檄文。辞意慷慨。此岂与闻叛逆之人耶。韩绚之言及此人者。只欲藉此。以诳诱愚民也。实不终始相通耳。此言出于金庆昌 张后载之招。臣于其时状 启略及之矣。踪迹未著。事状无疑。而竟死于栲掠之下。生膺忠勇之号。死于乱逆之狱。天下宁有是耶。自此以后。南方解体。无意御敌。臣于上年 除授本道监司。拜辞 引见时。请遣大臣于湖南。急急晓谕。收拾人心者。政为此也。
四留斋集卷之六 第 3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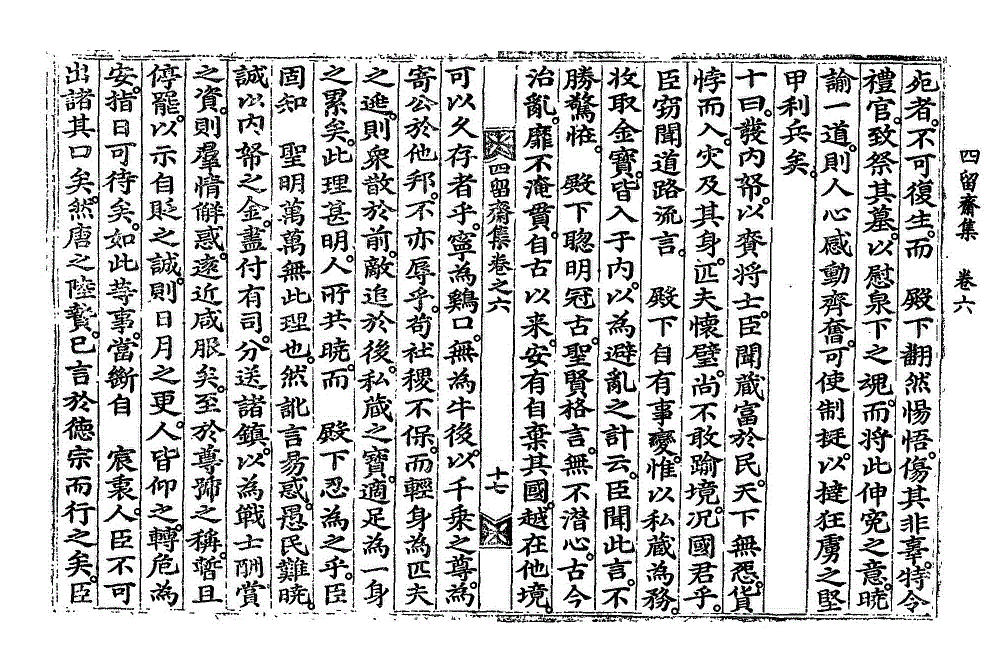 死者。不可复生。而 殿下翻然惕悟。伤其非辜。特令礼官。致祭其墓。以慰泉下之魂。而将此伸冤之意。晓谕一道。则人心感动齐奋。可使制挺。以挞狂虏之坚甲利兵矣。
死者。不可复生。而 殿下翻然惕悟。伤其非辜。特令礼官。致祭其墓。以慰泉下之魂。而将此伸冤之意。晓谕一道。则人心感动齐奋。可使制挺。以挞狂虏之坚甲利兵矣。十曰。发内帑。以赉将士。臣闻藏富于民。天下无怨。货悖而入。灾及其身。匹夫怀璧。尚不敢踰境。况国君乎。臣窃闻道路流言。殿下自有事变。惟以私藏为务。收取金宝。皆入于内。以为避乱之计云。臣闻此言。不胜惊怪。 殿下聪明冠古。圣贤格言。无不潜心。古今治乱。靡不淹贯。自古以来。安有自弃其国。越在他境。可以久存者乎。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以千乘之尊。为寄公于他邦。不亦辱乎。苟社稷不保。而轻身为匹夫之逃。则众散于前。敌追于后。私藏之宝。适足为一身之累矣。此理甚明。人所共晓。而 殿下忍为之乎。臣固知 圣明万万无此理也。然讹言易惑。愚民难晓。诚以内帑之金。尽付有司。分送诸镇。以为战士酬赏之资。则群情解惑。远近咸服矣。至于尊号之称。暂且停罢。以示自贬之诚。则日月之更。人皆仰之。转危为安。指日可待矣。如此等事。当断自 宸衷。人臣不可出诸其口矣。然唐之陆贽。已言于德宗而行之矣。臣
四留斋集卷之六 第 3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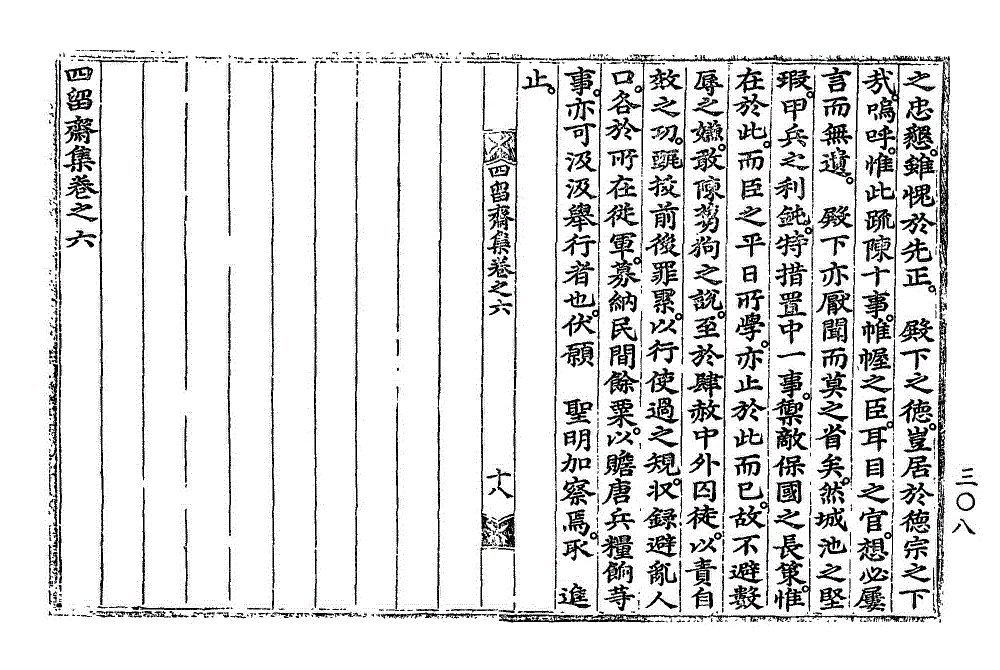 之忠恳。虽愧于先正。 殿下之德。岂居于德宗之下哉。呜呼。惟此疏陈十事。帷幄之臣。耳目之官。想必屡言而无遗。 殿下亦厌闻而莫之省矣。然城池之坚瑕。甲兵之利钝。特措置中一事。御敌保国之长策。惟在于此。而臣之平日所学。亦止于此而已。故不避数辱之嫌。敢陈刍狗之说。至于肆赦中外囚徒。以责自效之功。甄拔前后罪累。以行使过之规。收录避乱人口。各于所在从军。募纳民间馀粟。以赡唐兵粮饷等事。亦可汲汲举行者也。伏愿 圣明加察焉。取 进止。
之忠恳。虽愧于先正。 殿下之德。岂居于德宗之下哉。呜呼。惟此疏陈十事。帷幄之臣。耳目之官。想必屡言而无遗。 殿下亦厌闻而莫之省矣。然城池之坚瑕。甲兵之利钝。特措置中一事。御敌保国之长策。惟在于此。而臣之平日所学。亦止于此而已。故不避数辱之嫌。敢陈刍狗之说。至于肆赦中外囚徒。以责自效之功。甄拔前后罪累。以行使过之规。收录避乱人口。各于所在从军。募纳民间馀粟。以赡唐兵粮饷等事。亦可汲汲举行者也。伏愿 圣明加察焉。取 进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