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x 页
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杂著
杂著
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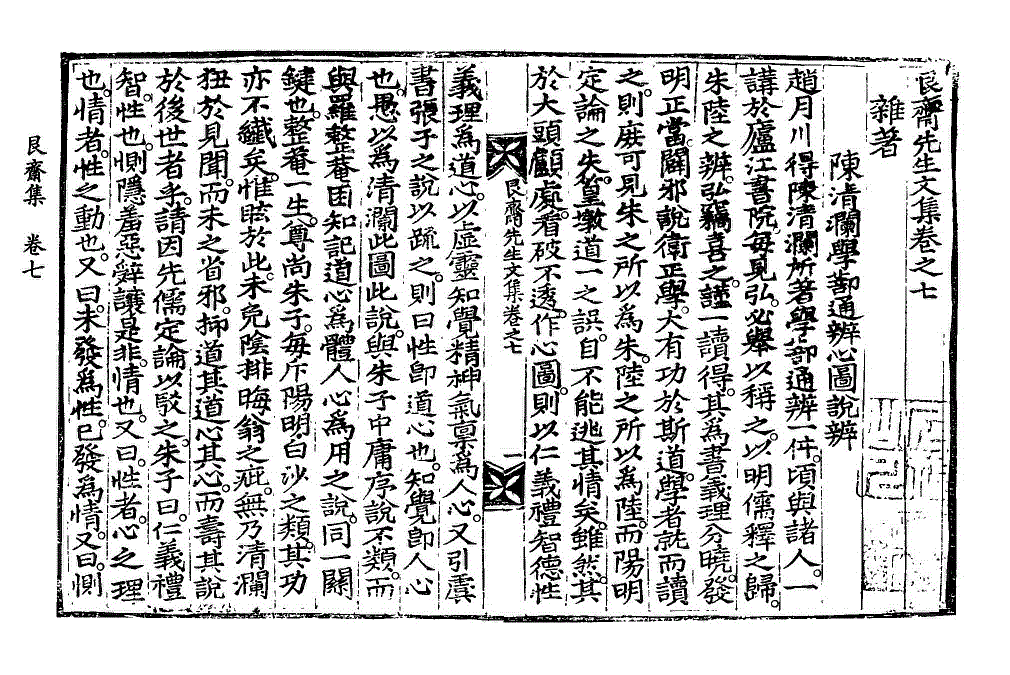 陈清澜学蔀通辨心图说辨
陈清澜学蔀通辨心图说辨赵月川得陈清澜所著学蔀通辨一件。顷与诸人。一讲于庐江书院。每见弘。必举以称之。以明儒释之归。朱陆之辨。弘窃喜之。谨一读得。其为书义理分晓。发明正当。辟邪说卫正学。大有功于斯道。学者就而读之。则庶可见朱之所以为朱。陆之所以为陆。而阳明定论之失。篁墩道一之误。自不能逃其情矣。虽然。其于大头颅处。看破不透。作心图。则以仁义礼智德性义理为道心。以虚灵知觉精神气禀为人心。又引虞书张子之说以疏之。则曰性即道心也。知觉即人心也。愚以为清澜此图此说。与朱子中庸序说不类。而与罗整庵困知记道心为体人心为用之说。同一关键也。整庵一生。尊尚朱子。每斥阳明白沙之类。其功亦不纤矣。惟眩于此。未免阴排晦翁之疵。无乃清澜狃于见闻。而未之省邪。抑道其道心其心。而寿其说于后世者乎。请因先儒定论以驳之。朱子曰。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又曰。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动也。又曰。未发为性。已发为情。又曰。恻
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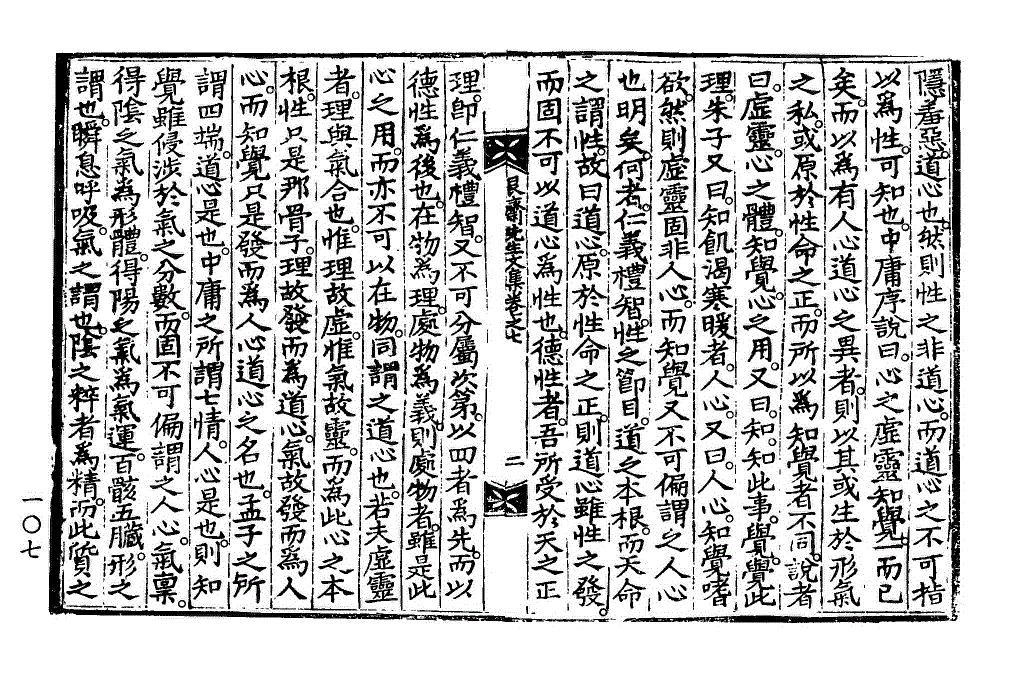 隐羞恶。道心也。然则性之非道心。而道心之不可指以为性。可知也。中庸序说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说者曰。虚灵。心之体。知觉。心之用。又曰。知。知此事。觉。觉此理。朱子又曰。知饥渴寒暖者。人心。又曰。人心。知觉嗜欲。然则虚灵固非人心。而知觉又不可偏谓之人心也明矣。何者。仁义礼智。性之节目。道之本根。而天命之谓性。故曰道心。原于性命之正。则道心虽性之发。而固不可以道心为性也。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即仁义礼智。又不可分属次第。以四者为先。而以德性为后也。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则处物者。虽是此心之用。而亦不可以在物。同谓之道心也。若夫虚灵者。理与气合也。惟理故虚。惟气故灵。而为此心之本根。性只是那骨子。理故发而为道心。气故发而为人心。而知觉只是发而为人心道心之名也。孟子之所谓四端。道心是也。中庸之所谓七情。人心是也。则知觉虽侵涉于气之分数。而固不可偏谓之人心。气禀。得阴之气为形体。得阳之气为气运。百骸五脏。形之谓也。瞬息呼吸。气之谓也。阴之粹者为精。而此质之
隐羞恶。道心也。然则性之非道心。而道心之不可指以为性。可知也。中庸序说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说者曰。虚灵。心之体。知觉。心之用。又曰。知。知此事。觉。觉此理。朱子又曰。知饥渴寒暖者。人心。又曰。人心。知觉嗜欲。然则虚灵固非人心。而知觉又不可偏谓之人心也明矣。何者。仁义礼智。性之节目。道之本根。而天命之谓性。故曰道心。原于性命之正。则道心虽性之发。而固不可以道心为性也。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即仁义礼智。又不可分属次第。以四者为先。而以德性为后也。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则处物者。虽是此心之用。而亦不可以在物。同谓之道心也。若夫虚灵者。理与气合也。惟理故虚。惟气故灵。而为此心之本根。性只是那骨子。理故发而为道心。气故发而为人心。而知觉只是发而为人心道心之名也。孟子之所谓四端。道心是也。中庸之所谓七情。人心是也。则知觉虽侵涉于气之分数。而固不可偏谓之人心。气禀。得阴之气为形体。得阳之气为气运。百骸五脏。形之谓也。瞬息呼吸。气之谓也。阴之粹者为精。而此质之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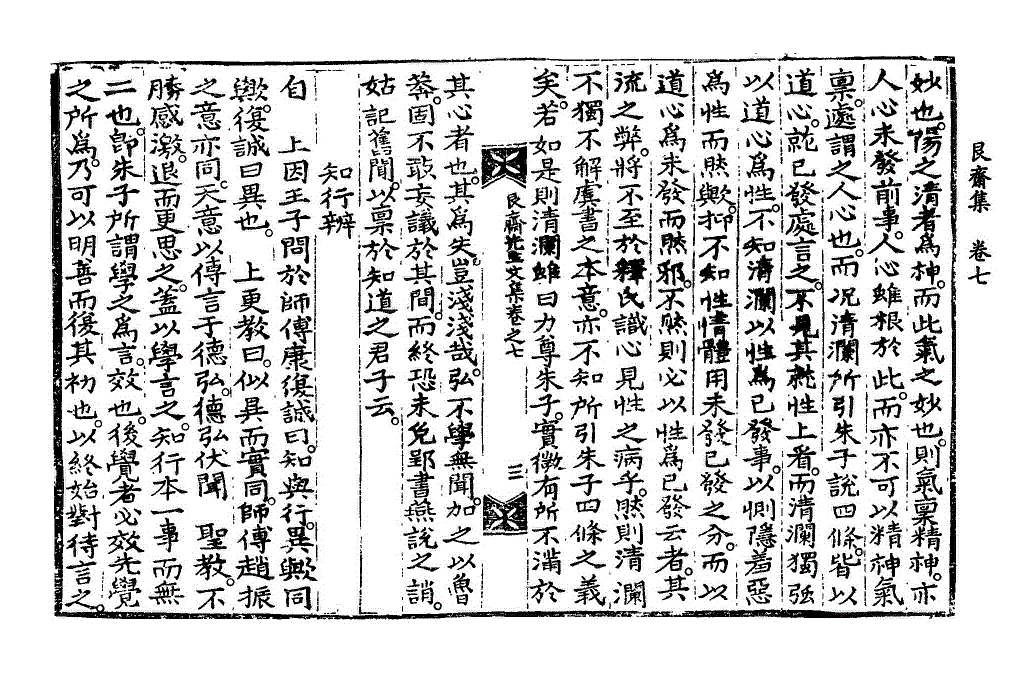 妙也。阳之清者为神。而此气之妙也。则气禀精神。亦人心未发前事。人心虽根于此。而亦不可以精神气禀。遽谓之人心也。而况清澜所引朱子说四条。皆以道心。就已发处言之。不见其就性上看。而清澜独强以道心为性。不知清澜以性为已发事。以恻隐羞恶为性而然欤。抑不知性情体用未发已发之分。而以道心为未发而然邪。不然则必以性为已发云者。其流之弊。将不至于释氏识心见性之病乎。然则清澜不独不解虞书之本意。亦不知所引朱子四条之义矣。若如是则清澜虽曰力尊朱子。实微有所不满于其心者也。其为失。岂浅浅哉。弘不学无闻。加之以鲁莽。固不敢妄议于其间。而终恐未免郢书燕说之诮。姑记旧闻。以禀于知道之君子云。
妙也。阳之清者为神。而此气之妙也。则气禀精神。亦人心未发前事。人心虽根于此。而亦不可以精神气禀。遽谓之人心也。而况清澜所引朱子说四条。皆以道心。就已发处言之。不见其就性上看。而清澜独强以道心为性。不知清澜以性为已发事。以恻隐羞恶为性而然欤。抑不知性情体用未发已发之分。而以道心为未发而然邪。不然则必以性为已发云者。其流之弊。将不至于释氏识心见性之病乎。然则清澜不独不解虞书之本意。亦不知所引朱子四条之义矣。若如是则清澜虽曰力尊朱子。实微有所不满于其心者也。其为失。岂浅浅哉。弘不学无闻。加之以鲁莽。固不敢妄议于其间。而终恐未免郢书燕说之诮。姑记旧闻。以禀于知道之君子云。知行辨
自上因王子问于师傅康复诚曰。知与行。异欤同欤。复诚曰异也。上更教曰。似异而实同。师傅赵振之意亦同。天意以传言于德弘。德弘伏闻圣教。不胜感激。退而更思之。盖以学言之。知行本一事而无二也。即朱子所谓学之为言。效也。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以终始对待言之。
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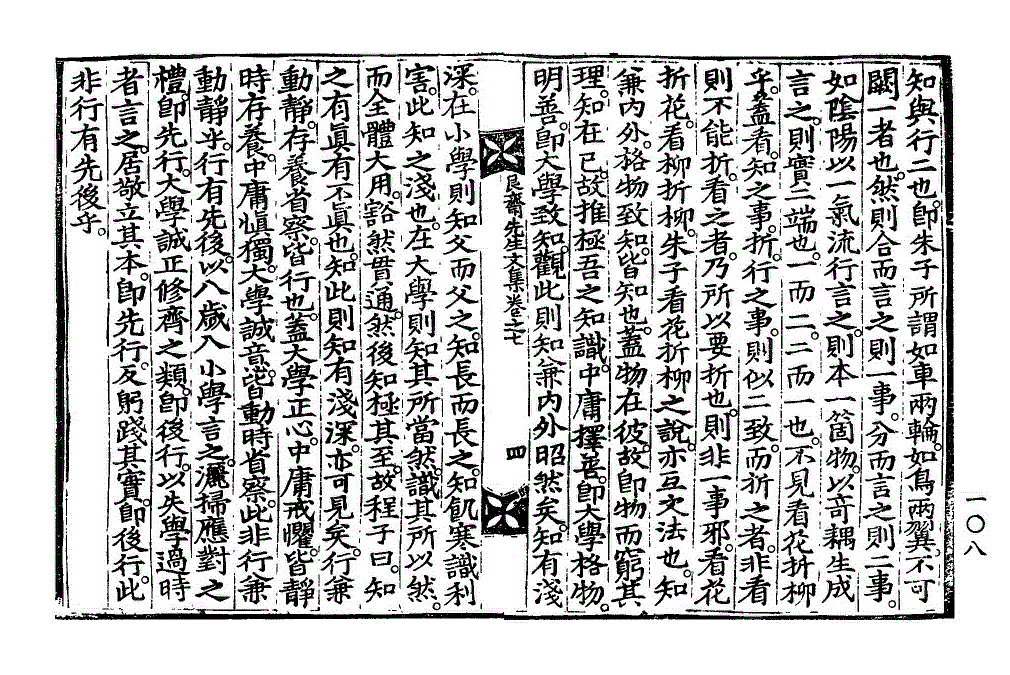 知与行二也。即朱子所谓如车两轮。如鸟两翼。不可阙一者也。然则合而言之则一事。分而言之则二事。如阴阳以一气流行言之。则本一个物。以奇耦生成言之。则实二端也。一而二。二而一也。不见看花折柳乎。盖看。知之事。折。行之事。则似二致。而折之者。非看则不能折。看之者。乃所以要折也。则非一事邪。看花折花。看柳折柳。朱子看花折柳之说。亦互文法也。知兼内外。格物致知。皆知也。盖物在彼。故即物而穷其理。知在己。故推极吾之知识。中庸择善。即大学格物。明善。即大学致知。观此则知兼内外昭然矣。知有浅深。在小学则知父而父之。知长而长之。知饥寒识利害。此知之浅也。在大学则知其所当然。识其所以然。而全体大用。豁然贯通。然后知极其至。故程子曰。知之有真有不真也。知此则知有浅深。亦可见矣。行兼动静。存养省察。皆行也。盖大学正心。中庸戒惧。皆静时存养。中庸慎独。大学诚意。皆动时省察。此非行兼动静乎。行有先后。以八岁入小学言之。洒扫应对之礼。即先行。大学诚正修齐之类。即后行。以失学过时者言之。居敬立其本。即先行。反躬践其实。即后行。此非行有先后乎。
知与行二也。即朱子所谓如车两轮。如鸟两翼。不可阙一者也。然则合而言之则一事。分而言之则二事。如阴阳以一气流行言之。则本一个物。以奇耦生成言之。则实二端也。一而二。二而一也。不见看花折柳乎。盖看。知之事。折。行之事。则似二致。而折之者。非看则不能折。看之者。乃所以要折也。则非一事邪。看花折花。看柳折柳。朱子看花折柳之说。亦互文法也。知兼内外。格物致知。皆知也。盖物在彼。故即物而穷其理。知在己。故推极吾之知识。中庸择善。即大学格物。明善。即大学致知。观此则知兼内外昭然矣。知有浅深。在小学则知父而父之。知长而长之。知饥寒识利害。此知之浅也。在大学则知其所当然。识其所以然。而全体大用。豁然贯通。然后知极其至。故程子曰。知之有真有不真也。知此则知有浅深。亦可见矣。行兼动静。存养省察。皆行也。盖大学正心。中庸戒惧。皆静时存养。中庸慎独。大学诚意。皆动时省察。此非行兼动静乎。行有先后。以八岁入小学言之。洒扫应对之礼。即先行。大学诚正修齐之类。即后行。以失学过时者言之。居敬立其本。即先行。反躬践其实。即后行。此非行有先后乎。造化辨
造化之为造化者。幽明屈伸而已。天者。明而伸者也。地者。幽而屈者也。暑者。明而伸者也。寒者。幽而屈者也。昼者。明而伸者也。夜者。幽而屈者也。天地也寒暑也昼夜也。幽明屈伸。而以成变化者也。是故。阳者吐气。阴者含气。吐气者施。含气者化。阳施阴化。而人道立。万物繁矣。阳薄阴则绕而为风。阴囚阳则奋而为雷。阳和阴则为雨为露。阴和阳则为霜为雪。阴阳不和则为戾气也。
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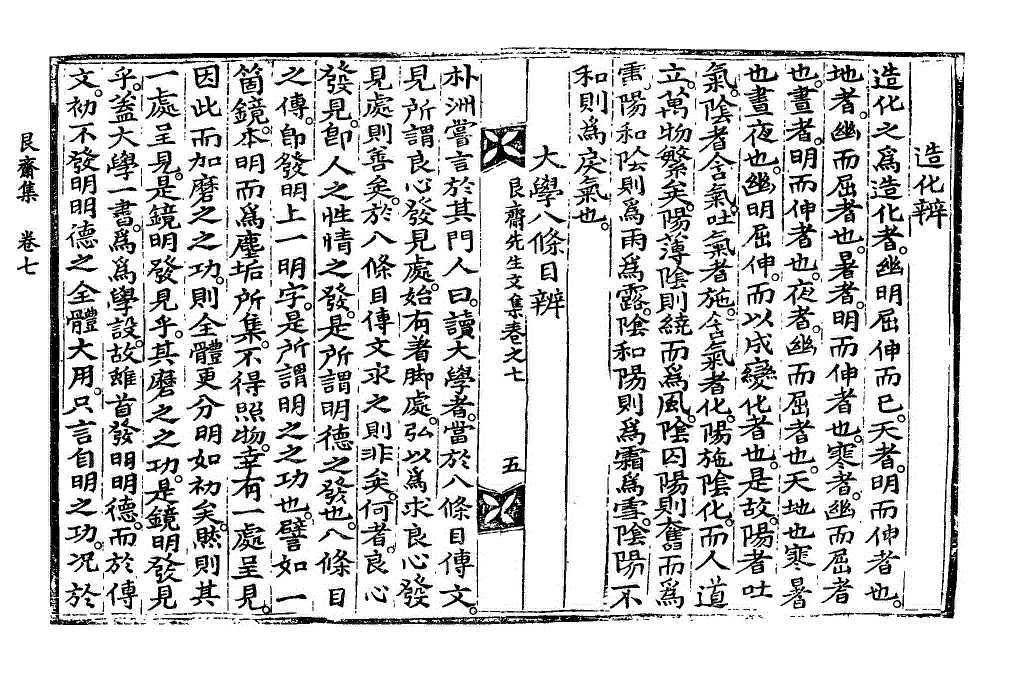 大学八条目辨
大学八条目辨朴洲尝言于其门人曰。读大学者。当于八条目传文。见所谓良心发见处。始有着脚处。弘以为求良心发见处则善矣。于八条目传文求之则非矣。何者。良心发见。即人之性情之发。是所谓明德之发也。八条目之传。即发明上一明字。是所谓明之之功也。譬如一个镜。本明而为尘垢所集。不得照物。幸有一处呈见。因此而加磨之之功。则全体更分明如初矣。然则其一处呈见。是镜明发见乎。其磨之之功。是镜明发见乎。盖大学一书。为为学说。故虽首发明明德。而于传文。初不发明明德之全体大用。只言自明之功。况于
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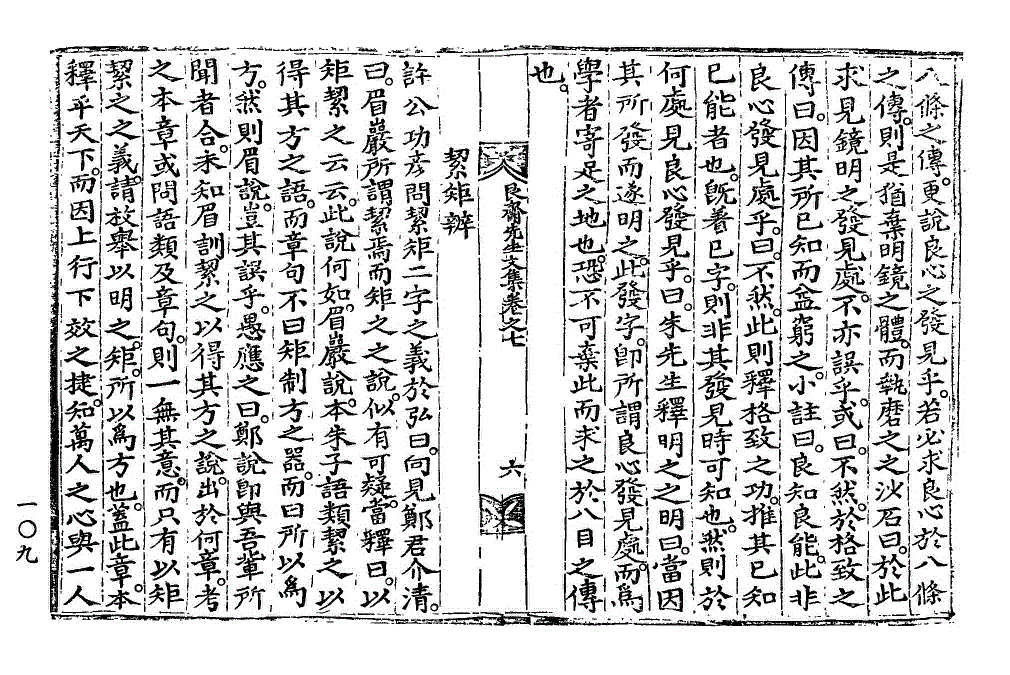 八条之传。更说良心之发见乎。若必求良心于八条之传。则是犹弃明镜之体。而执磨之之沙石曰。于此求见镜明之发见处。不亦误乎。或曰。不然。于格致之传曰。因其所已知而益穷之。小注曰。良知良能。此非良心发见处乎。曰。不然。此则释格致之功。推其已知已能者也。既著已字。则非其发见时可知也。然则于何处见良心发见乎。曰。朱先生释明之之明曰。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此发字。即所谓良心发见处。而为学者寄足之地也。恐不可弃此而求之于八目之传也。
八条之传。更说良心之发见乎。若必求良心于八条之传。则是犹弃明镜之体。而执磨之之沙石曰。于此求见镜明之发见处。不亦误乎。或曰。不然。于格致之传曰。因其所已知而益穷之。小注曰。良知良能。此非良心发见处乎。曰。不然。此则释格致之功。推其已知已能者也。既著已字。则非其发见时可知也。然则于何处见良心发见乎。曰。朱先生释明之之明曰。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此发字。即所谓良心发见处。而为学者寄足之地也。恐不可弃此而求之于八目之传也。絜矩辨
许公功彦问絜矩二字之义于弘曰。向见郑君介清。曰。眉岩所谓絜焉而矩之之说。似有可疑。当释曰。以矩絜之云云。此说何如。眉岩说。本朱子语类絜之以得其方之语。而章句不曰矩制方之器。而曰所以为方。然则眉说。岂其误乎。愚应之曰。郑说即与吾辈所闻者合。未知眉训絜之以得其方之说。出于何章。考之本章或问语类及章句。则一无其意。而只有以矩絜之之义。请枚举以明之。矩。所以为方也。盖此章。本释乎天下。而因上行下效之捷。知万人之心与一人
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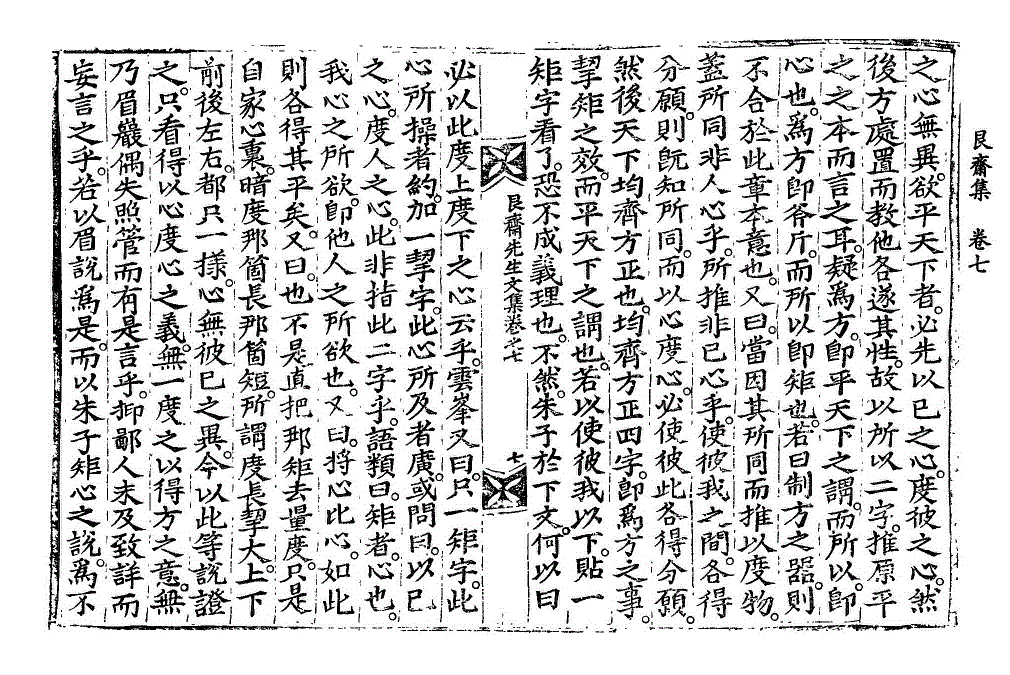 之心无异。欲平天下者。必先以己之心。度彼之心。然后方处置而教他各遂其性。故以所以二字。推原平之之本而言之耳。疑为方。即平天下之谓。而所以。即心也。为方即斧斤。而所以即矩也。若曰制方之器。则不合于此章本意也。又曰。当因其所同而推以度物。盖所同非人心乎。所推非己心乎。使彼我之间。各得分愿。则既知所同。而以心度心。必使彼此各得分愿。然后天下均齐方正也。均齐方正四字。即为方之事。絜矩之效。而平天下之谓也。若以使彼我以下。贴一矩字看了。恐不成义理也。不然。朱子于下文。何以曰必以此度上度下之心云乎。云峰又曰。只一矩字。此心所操者约。加一絜字。此心所及者广。或问曰。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此非指此二字乎。语类曰。矩者。心也。我心之所欲。即他人之所欲也。又曰。将心比心。如此则各得其平矣。又曰。也不是直把那矩去量度。只是自家心里。暗度那个长那个短。所谓度长絜大。上下前后左右。都只一㨾。心无彼己之异。今以此等说證之。只看得以心度心之义。无一度之以得方之意。无乃眉岩偶失照管而有是言乎。抑鄙人未及致详而妄言之乎。若以眉说为是。而以朱子矩心之说。为不
之心无异。欲平天下者。必先以己之心。度彼之心。然后方处置而教他各遂其性。故以所以二字。推原平之之本而言之耳。疑为方。即平天下之谓。而所以。即心也。为方即斧斤。而所以即矩也。若曰制方之器。则不合于此章本意也。又曰。当因其所同而推以度物。盖所同非人心乎。所推非己心乎。使彼我之间。各得分愿。则既知所同。而以心度心。必使彼此各得分愿。然后天下均齐方正也。均齐方正四字。即为方之事。絜矩之效。而平天下之谓也。若以使彼我以下。贴一矩字看了。恐不成义理也。不然。朱子于下文。何以曰必以此度上度下之心云乎。云峰又曰。只一矩字。此心所操者约。加一絜字。此心所及者广。或问曰。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此非指此二字乎。语类曰。矩者。心也。我心之所欲。即他人之所欲也。又曰。将心比心。如此则各得其平矣。又曰。也不是直把那矩去量度。只是自家心里。暗度那个长那个短。所谓度长絜大。上下前后左右。都只一㨾。心无彼己之异。今以此等说證之。只看得以心度心之义。无一度之以得方之意。无乃眉岩偶失照管而有是言乎。抑鄙人未及致详而妄言之乎。若以眉说为是。而以朱子矩心之说。为不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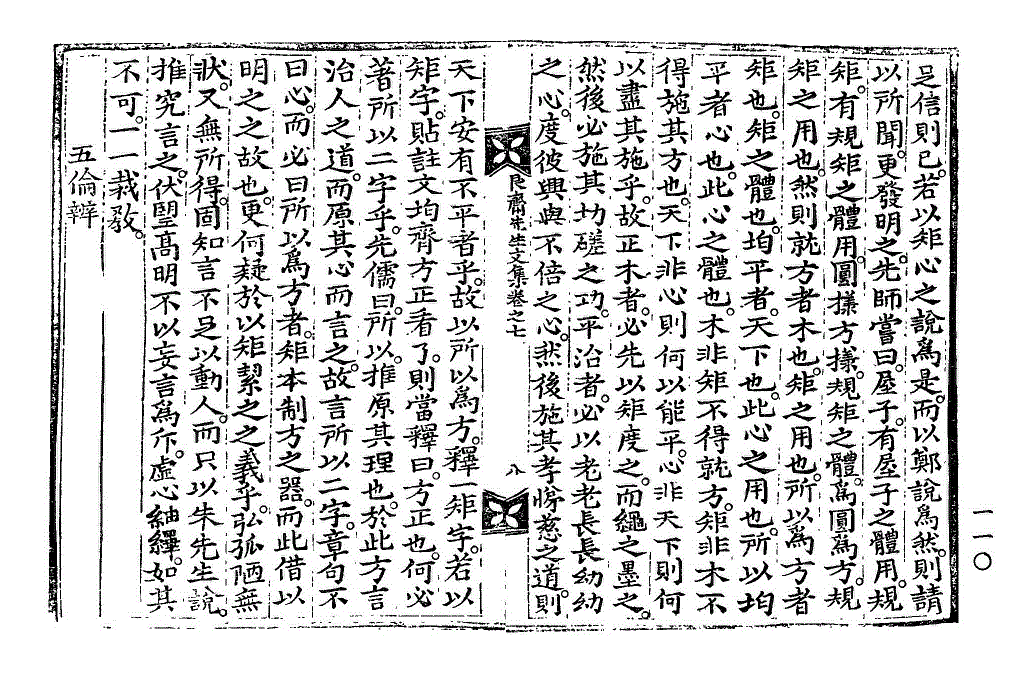 足信则已。若以矩心之说为是。而以郑说为然。则请以所闻。更发明之。先师尝曰。屋子。有屋子之体用。规矩。有规矩之体用。圆㨾方㨾。规矩之体。为圆为方。规矩之用也。然则就方者木也。矩之用也。所以为方者矩也。矩之体也。均平者。天下也。此心之用也。所以均平者心也。此心之体也。木非矩不得就方。矩非木不得施其方也。天下非心则何以能平。心非天下则何以尽其施乎。故正木者。必先以矩度之。而绳之墨之。然后必施其切磋之功。平治者。必以老老长长幼幼之心。度彼兴与不倍之心。然后施其孝悌慈之道。则天下安有不平者乎。故以所以为方。释一矩字。若以矩字。贴注文均齐方正看了。则当释曰。方正也。何必著所以二字乎。先儒曰。所以。推原其理也。于此方言治人之道。而原其心而言之。故言所以二字。章句不曰心。而必曰所以为方者。矩本制方之器。而此借以明之之故也。更何疑于以矩絜之之义乎。弘孤陋无状。又无所得。固知言不足以动人。而只以朱先生说。推究言之。伏望高明不以妄言为斥。虚心䌷绎。如其不可。一一裁教。
足信则已。若以矩心之说为是。而以郑说为然。则请以所闻。更发明之。先师尝曰。屋子。有屋子之体用。规矩。有规矩之体用。圆㨾方㨾。规矩之体。为圆为方。规矩之用也。然则就方者木也。矩之用也。所以为方者矩也。矩之体也。均平者。天下也。此心之用也。所以均平者心也。此心之体也。木非矩不得就方。矩非木不得施其方也。天下非心则何以能平。心非天下则何以尽其施乎。故正木者。必先以矩度之。而绳之墨之。然后必施其切磋之功。平治者。必以老老长长幼幼之心。度彼兴与不倍之心。然后施其孝悌慈之道。则天下安有不平者乎。故以所以为方。释一矩字。若以矩字。贴注文均齐方正看了。则当释曰。方正也。何必著所以二字乎。先儒曰。所以。推原其理也。于此方言治人之道。而原其心而言之。故言所以二字。章句不曰心。而必曰所以为方者。矩本制方之器。而此借以明之之故也。更何疑于以矩絜之之义乎。弘孤陋无状。又无所得。固知言不足以动人。而只以朱先生说。推究言之。伏望高明不以妄言为斥。虚心䌷绎。如其不可。一一裁教。五伦辨
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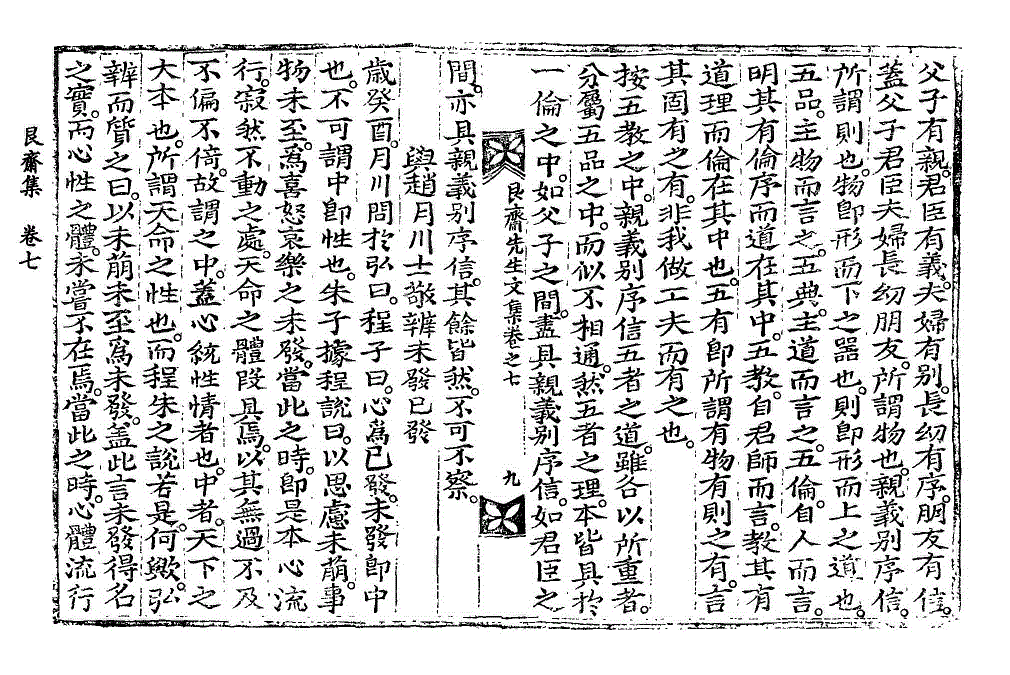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盖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所谓物也。亲义别序信。所谓则也。物即形而下之器也。则即形而上之道也。五品。主物而言之。五典。主道而言之。五伦。自人而言。明其有伦序而道在其中。五教。自君师而言。教其有道理而伦在其中也。五有即所谓有物有则之有。言其固有之有。非我做工夫而有之也。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盖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所谓物也。亲义别序信。所谓则也。物即形而下之器也。则即形而上之道也。五品。主物而言之。五典。主道而言之。五伦。自人而言。明其有伦序而道在其中。五教。自君师而言。教其有道理而伦在其中也。五有即所谓有物有则之有。言其固有之有。非我做工夫而有之也。按五教之中。亲义别序信五者之道。虽各以所重者。分属五品之中。而似不相通。然五者之理。本皆具于一伦之中。如父子之间。尽具亲义别序信。如君臣之间。亦具亲义别序信。其馀皆然。不可不察。
与赵月川士敬辨未发已发
岁癸酉。月川问于弘曰。程子曰。心为已发。未发即中也。不可谓中即性也。朱子据程说曰。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本心流行。寂然不动之处。天命之体段具焉。以其无过不及不偏不倚。故谓之中。盖心统性情者也。中者。天下之大本也。所谓天命之性也。而程朱之说若是。何欤。弘辨而质之曰。以未萌未至为未发。盖此言未发得名之实。而心性之体。未尝不在焉。当此之时。心体流行
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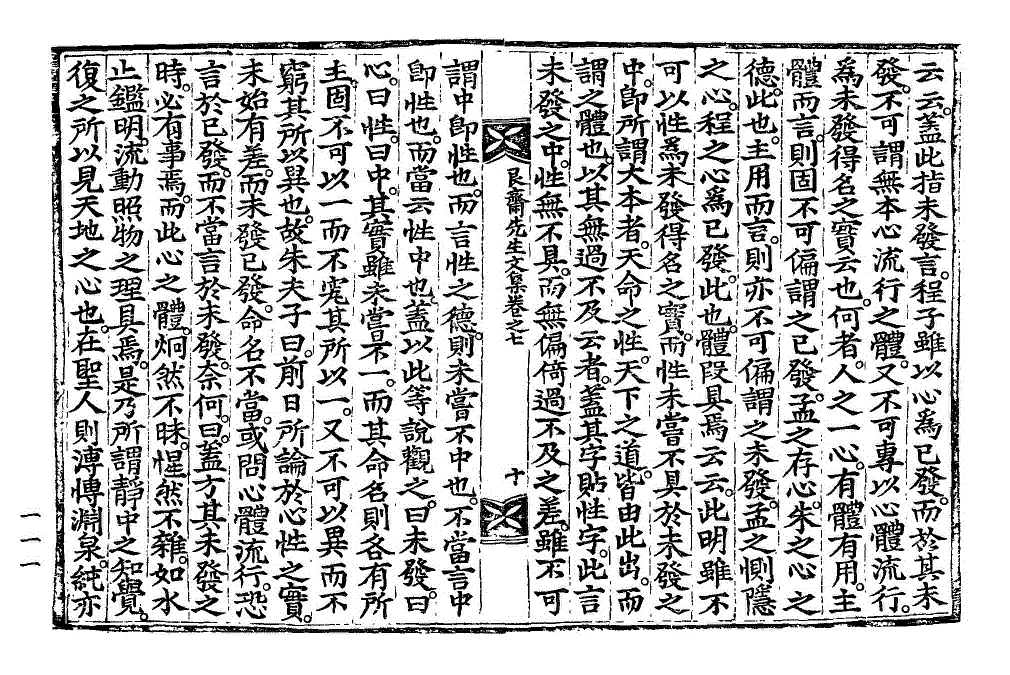 云云。盖此指未发言。程子虽以心为已发。而于其未发。不可谓无本心流行之体。又不可专以心体流行。为未发得名之实云也。何者。人之一心。有体有用。主体而言。则固不可偏谓之已发。孟之存心。朱之心之德。此也。主用而言。则亦不可偏谓之未发。孟之恻隐之心。程之心为已发。此也。体段具焉云云。此明虽不可以性为未发得名之实。而性未尝不具于未发之中。即所谓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道。皆由此出。而谓之体也。以其无过不及云者。盖其字贴性字。此言未发之中。性无不具。而无偏倚过不及之差。虽不可谓中即性也。而言性之德。则未尝不中也。不当言中即性也。而当云性中也。盖以此等说观之。曰未发。曰心。曰性。曰中。其实虽未尝不一。而其命名则各有所主。固不可以一而不究其所以一。又不可以异而不穷其所以异也。故朱夫子曰。前日所论于心性之实。未始有差。而未发已发。命名不当。或问心体流行。恐言于已发。而不当言于未发。奈何。曰。盖方其未发之时。必有事焉。而此心之体。炯然不昩。惺然不杂。如水止鉴明。流动照物之理具焉。是乃所谓静中之知觉。复之所以见天地之心也。在圣人则溥博渊泉。纯亦
云云。盖此指未发言。程子虽以心为已发。而于其未发。不可谓无本心流行之体。又不可专以心体流行。为未发得名之实云也。何者。人之一心。有体有用。主体而言。则固不可偏谓之已发。孟之存心。朱之心之德。此也。主用而言。则亦不可偏谓之未发。孟之恻隐之心。程之心为已发。此也。体段具焉云云。此明虽不可以性为未发得名之实。而性未尝不具于未发之中。即所谓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道。皆由此出。而谓之体也。以其无过不及云者。盖其字贴性字。此言未发之中。性无不具。而无偏倚过不及之差。虽不可谓中即性也。而言性之德。则未尝不中也。不当言中即性也。而当云性中也。盖以此等说观之。曰未发。曰心。曰性。曰中。其实虽未尝不一。而其命名则各有所主。固不可以一而不究其所以一。又不可以异而不穷其所以异也。故朱夫子曰。前日所论于心性之实。未始有差。而未发已发。命名不当。或问心体流行。恐言于已发。而不当言于未发。奈何。曰。盖方其未发之时。必有事焉。而此心之体。炯然不昩。惺然不杂。如水止鉴明。流动照物之理具焉。是乃所谓静中之知觉。复之所以见天地之心也。在圣人则溥博渊泉。纯亦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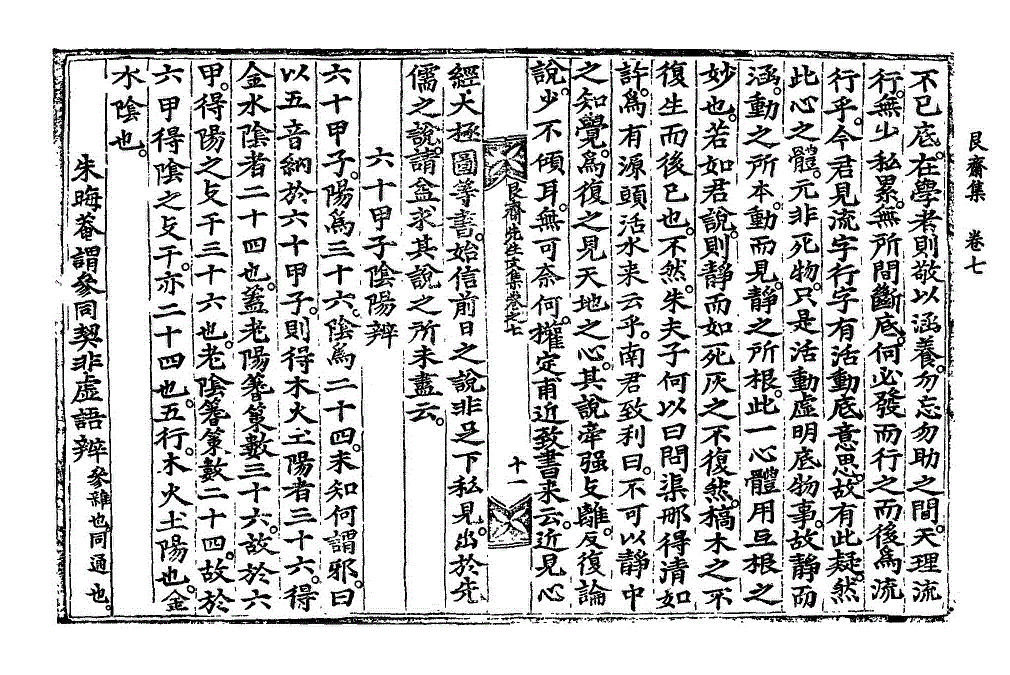 不已底。在学者则敬以涵养。勿忘勿助之间。天理流行。无少私累。无所间断底。何必发而行之而后为流行乎。今君见流字行字有活动底意思。故有此疑。然此心之体。元非死物。只是活动虚明底物事。故静而涵。动之所本。动而见。静之所根。此一心体用互根之妙也。若如君说。则静而如死灰之不复然。槁木之不复生而后已也。不然。朱夫子何以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云乎。南君致利曰。不可以静中之知觉。为复之见天地之心。其说牵强支离。反复论说。少不倾耳。无可奈何。权定甫近致书来云。近见心经太极图等书。始信前日之说非足下私见。出于先儒之说。请益求其说之所未尽云。
不已底。在学者则敬以涵养。勿忘勿助之间。天理流行。无少私累。无所间断底。何必发而行之而后为流行乎。今君见流字行字有活动底意思。故有此疑。然此心之体。元非死物。只是活动虚明底物事。故静而涵。动之所本。动而见。静之所根。此一心体用互根之妙也。若如君说。则静而如死灰之不复然。槁木之不复生而后已也。不然。朱夫子何以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云乎。南君致利曰。不可以静中之知觉。为复之见天地之心。其说牵强支离。反复论说。少不倾耳。无可奈何。权定甫近致书来云。近见心经太极图等书。始信前日之说非足下私见。出于先儒之说。请益求其说之所未尽云。六十甲子阴阳辨
六十甲子。阳为三十六。阴为二十四。未知何谓邪。曰以五音纳于六十甲子。则得木火土阳者三十六。得金水阴者二十四也。盖老阳蓍策数三十六。故于六甲。得阳之支干三十六也。老阴蓍策数二十四。故于六甲得阴之支干。亦二十四也。五行。木火土阳也。金水阴也。
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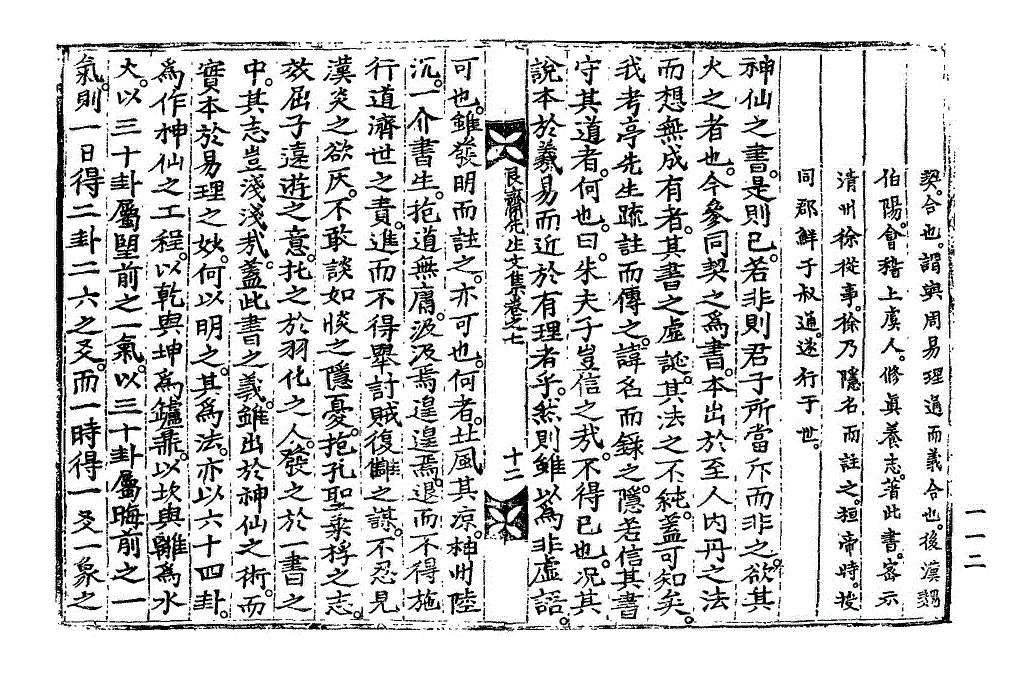 朱晦庵谓参同契非虚语辨(参杂也。同通也。契。合也。谓与周易理通而义合也。后汉魏伯阳。会稽上虞人。修真养志。著此书。密示清州徐从事。徐乃隐名而注之。桓帝时。授同郡鲜于叔通。遂行于世。)
朱晦庵谓参同契非虚语辨(参杂也。同通也。契。合也。谓与周易理通而义合也。后汉魏伯阳。会稽上虞人。修真养志。著此书。密示清州徐从事。徐乃隐名而注之。桓帝时。授同郡鲜于叔通。遂行于世。)神仙之书。是则已。若非则君子所当斥而非之。欲其火之者也。今参同契之为书。本出于至人内丹之法而想无成有者。其书之虚诞。其法之不纯。盖可知矣。我考亭先生疏注而传之。讳名而录之。隐若信其书守其道者。何也。曰。朱夫子岂信之哉。不得已也。况其说本于羲易而近于有理者乎。然则虽以为非虚语。可也。虽发明而注之。亦可也。何者。北风其凉。神州陆沉。一介书生。抱道无庸。汲汲焉遑遑焉。退而不得施行道济世之责。进而不得举讨贼复雠之谋。不忍见汉炎之欲灰。不敢谈如惔之隐忧。抱孔圣乘桴之志。效屈子远游之意。托之于羽化之人。发之于一书之中。其志岂浅浅哉。盖此书之义。虽出于神仙之术。而实本于易理之妙。何以明之。其为法。亦以六十四卦。为作神仙之工程。以乾与坤为垆鼎。以坎与离为水火。以三十卦属望前之一气。以三十卦属晦前之一气。则一日得二卦二六之爻。而一时得一爻一象之
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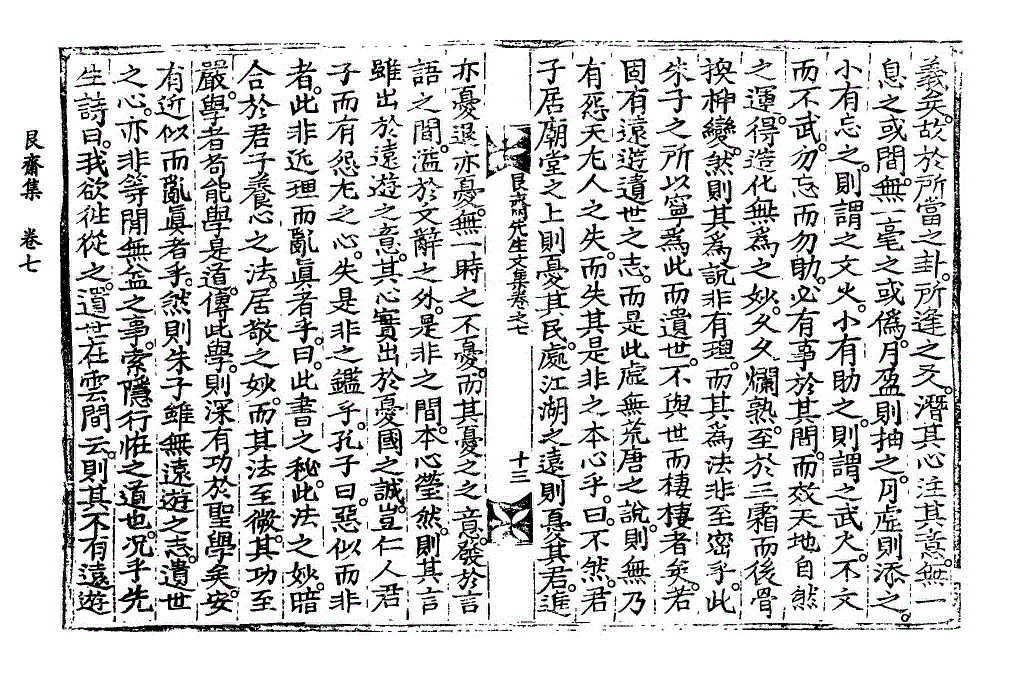 义矣。故于所当之卦。所逢之爻。潜其心注其意。无一息之或间。无一毫之或伪。月盈则抽之。月虚则添之。小有忘之。则谓之文火。小有助之。则谓之武火。不文而不武。勿忘而勿助。必有事于其间。而效天地自然之运。得造化无为之妙。久久烂熟。至于三霜而后骨换神变。然则其为说非有理。而其为法非至密乎。此朱子之所以宁为此而遗世。不与世而栖栖者矣。若固有远游遗世之志。而是此虚无荒唐之说。则无乃有怨天尤人之失。而失其是非之本心乎。曰。不然。君子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无一时之不忧。而其忧之之意。发于言语之间。溢于文辞之外。是非之间。本心莹然。则其言虽出于远游之意。其心实出于忧国之诚。岂仁人君子而有怨尤之心。失是非之鉴乎。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此非近理而乱真者乎。曰。此书之秘。此法之妙。暗合于君子养心之法。居敬之妙。而其法至微。其功至严。学者苟能学是道。传此学。则深有功于圣学矣。安有近似而乱真者乎。然则失子虽无远游之志。遗世之心。亦非等閒无益之事。索隐行怪之道也。况乎先生诗曰。我欲往从之。遗世在云间云。则其不有远游
义矣。故于所当之卦。所逢之爻。潜其心注其意。无一息之或间。无一毫之或伪。月盈则抽之。月虚则添之。小有忘之。则谓之文火。小有助之。则谓之武火。不文而不武。勿忘而勿助。必有事于其间。而效天地自然之运。得造化无为之妙。久久烂熟。至于三霜而后骨换神变。然则其为说非有理。而其为法非至密乎。此朱子之所以宁为此而遗世。不与世而栖栖者矣。若固有远游遗世之志。而是此虚无荒唐之说。则无乃有怨天尤人之失。而失其是非之本心乎。曰。不然。君子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无一时之不忧。而其忧之之意。发于言语之间。溢于文辞之外。是非之间。本心莹然。则其言虽出于远游之意。其心实出于忧国之诚。岂仁人君子而有怨尤之心。失是非之鉴乎。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此非近理而乱真者乎。曰。此书之秘。此法之妙。暗合于君子养心之法。居敬之妙。而其法至微。其功至严。学者苟能学是道。传此学。则深有功于圣学矣。安有近似而乱真者乎。然则失子虽无远游之志。遗世之心。亦非等閒无益之事。索隐行怪之道也。况乎先生诗曰。我欲往从之。遗世在云间云。则其不有远游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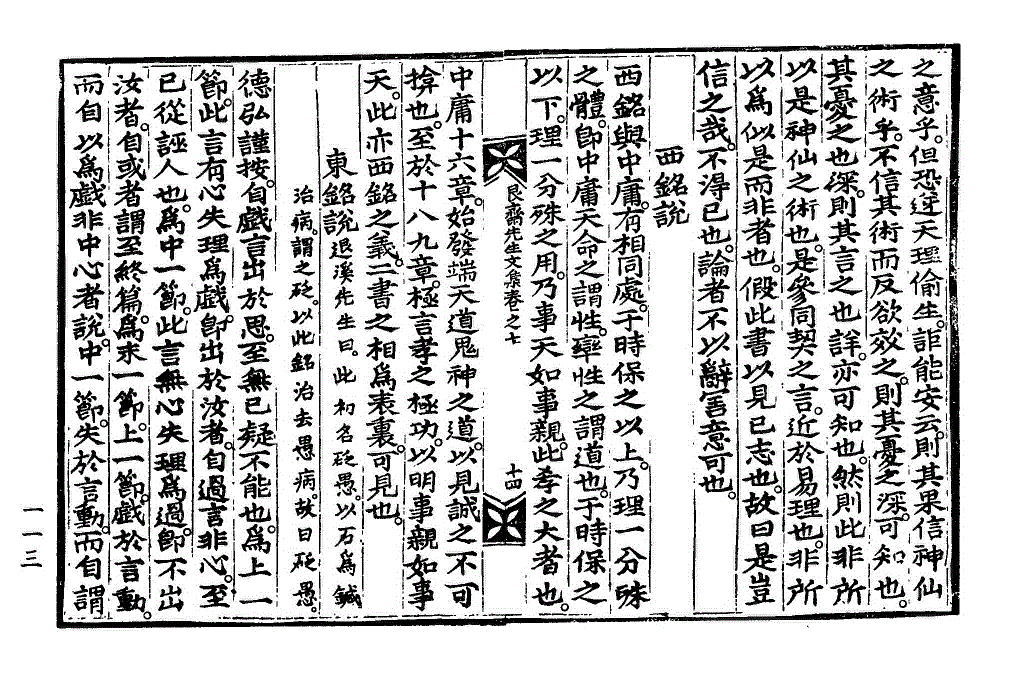 之意乎。但恐逆天理偷生。讵能安云。则其果信神仙之术乎。不信其术而反欲效之。则其忧之深。可知也。其忧之也深。则其言之也详。亦可知也。然则此非所以是神仙之术也。是参同契之言。近于易理也。非所以为似是而非者也。假此书以见己志也。故曰是岂信之哉。不得已也。论者不以辞害意可也。
之意乎。但恐逆天理偷生。讵能安云。则其果信神仙之术乎。不信其术而反欲效之。则其忧之深。可知也。其忧之也深。则其言之也详。亦可知也。然则此非所以是神仙之术也。是参同契之言。近于易理也。非所以为似是而非者也。假此书以见己志也。故曰是岂信之哉。不得已也。论者不以辞害意可也。西铭说
西铭与中庸。有相同处。于时保之以上。乃理一分殊之体。即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也。于时保之以下。理一分殊之用。乃事天如事亲。此孝之大者也。中庸十六章。始发端天道鬼神之道。以见诚之不可掩也。至于十八九章。极言孝之极功。以明事亲如事天。此亦西铭之义。二书之相为表里。可见也。
东铭说(退溪先生曰。此初名砭愚。以石为针治病。谓之砭。以此铭治去愚病。故曰砭愚。)
德弘谨按。自戏言出于思。至无己疑不能也。为上一节。此言有心失理为戏。即出于汝者。自过言非心。至己从诬人也。为中一节。此言无心失理为过。即不出汝者。自或者谓至终篇。为末一节。上一节。戏于言动。而自以为戏非中心者说。中一节。失于言动。而自谓
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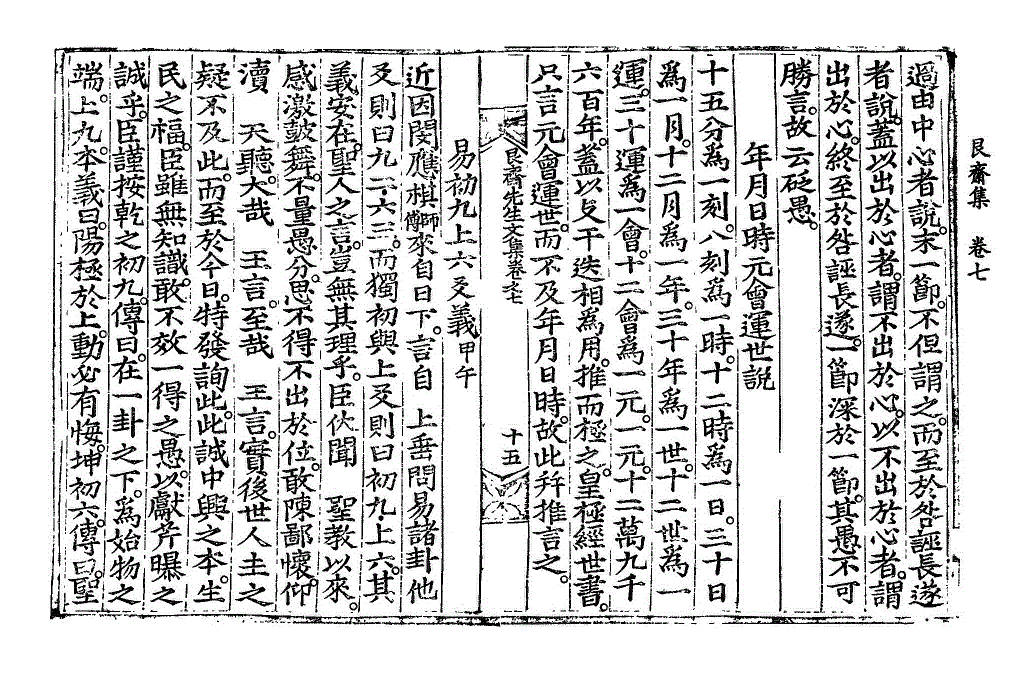 过由中心者说。末一节。不但谓之。而至于咎诬长遂者说。盖以出于心者。谓不出于心。以不出于心者。谓出于心。终至于咎诬长遂。一节深于一节。其愚不可胜言。故云砭愚。
过由中心者说。末一节。不但谓之。而至于咎诬长遂者说。盖以出于心者。谓不出于心。以不出于心者。谓出于心。终至于咎诬长遂。一节深于一节。其愚不可胜言。故云砭愚。年月日时云会运世说
十五分为一刻。八刻为一时。十二时为一日。三十日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年。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一元。十二万九千六百年。盖以支干迭相为用。推而极之。皇极经世书。只言元会运世。而不及年月日时。故此并推言之。
易初九上六爻义(甲午)
近因闵应祺(师傅)来自日下。言自上垂问易诸卦他爻则曰九二,六三。而独初与上爻则曰初九,上六。其义安在。圣人之言。岂无其理乎。臣伏闻圣教以来。感激鼓舞。不量愚分。思不得不出于位。敢陈鄙怀。仰渎天听。大哉王言。至哉王言。实后世人主之疑不及此。而至于今日。特发询此。此诚中兴之本。生民之福。臣虽无知识。敢不效一得之愚。以献芹曝之诚乎。臣谨按乾之初九。传曰。在一卦之下。为始物之端。上九。本义曰。阳极于上。动必有悔。坤初六。传曰。圣
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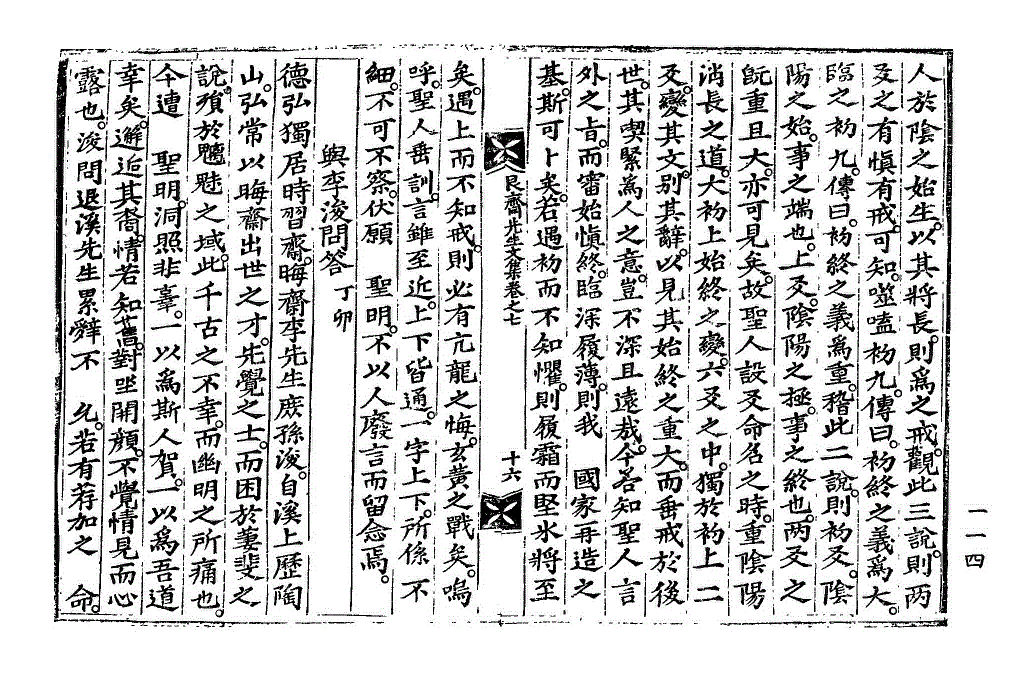 人于阴之始生。以其将长。则为之戒。观此三说。则两爻之有慎有戒。可知。噬嗑初九。传曰。初终之义为大。临之初九。传曰。初终之义为重。稽此二说。则初爻。阴阳之始。事之端也。上爻。阴阳之极。事之终也。两爻之既重且大。亦可见矣。故圣人设爻命名之时。重阴阳消长之道。大初上始终之变。六爻之中。独于初上二爻。变其文。别其辞。以见其始终之重大。而垂戒于后世。其吃紧为人之意。岂不深且远哉。今若知圣人言外之旨。而审始慎终。临深履薄。则我国家再造之基。斯可卜矣。若遇初而不知惧。则履霜而坚冰将至矣。遇上而不知戒。则必有亢龙之悔。玄黄之战矣。呜呼。圣人垂训。言虽至近。上下皆通。一字上下。所系不细。不可不察。伏愿圣明。不以人废言而留念焉。
人于阴之始生。以其将长。则为之戒。观此三说。则两爻之有慎有戒。可知。噬嗑初九。传曰。初终之义为大。临之初九。传曰。初终之义为重。稽此二说。则初爻。阴阳之始。事之端也。上爻。阴阳之极。事之终也。两爻之既重且大。亦可见矣。故圣人设爻命名之时。重阴阳消长之道。大初上始终之变。六爻之中。独于初上二爻。变其文。别其辞。以见其始终之重大。而垂戒于后世。其吃紧为人之意。岂不深且远哉。今若知圣人言外之旨。而审始慎终。临深履薄。则我国家再造之基。斯可卜矣。若遇初而不知惧。则履霜而坚冰将至矣。遇上而不知戒。则必有亢龙之悔。玄黄之战矣。呜呼。圣人垂训。言虽至近。上下皆通。一字上下。所系不细。不可不察。伏愿圣明。不以人废言而留念焉。与李浚问答(丁卯)
德弘独居时习斋。晦斋李先生庶孙浚。自溪上历陶山。弘常以晦斋出世之才。先觉之士。而困于萋斐之说。殒于魑魅之域。此千古之不幸。而幽明之所痛也。今遭圣明。洞照非辜。一以为斯人贺。一以为吾道幸矣。邂逅其裔。情若知旧。对坐开颜。不觉情见而心露也。浚问退溪先生累辞不允。若有荐加之命。
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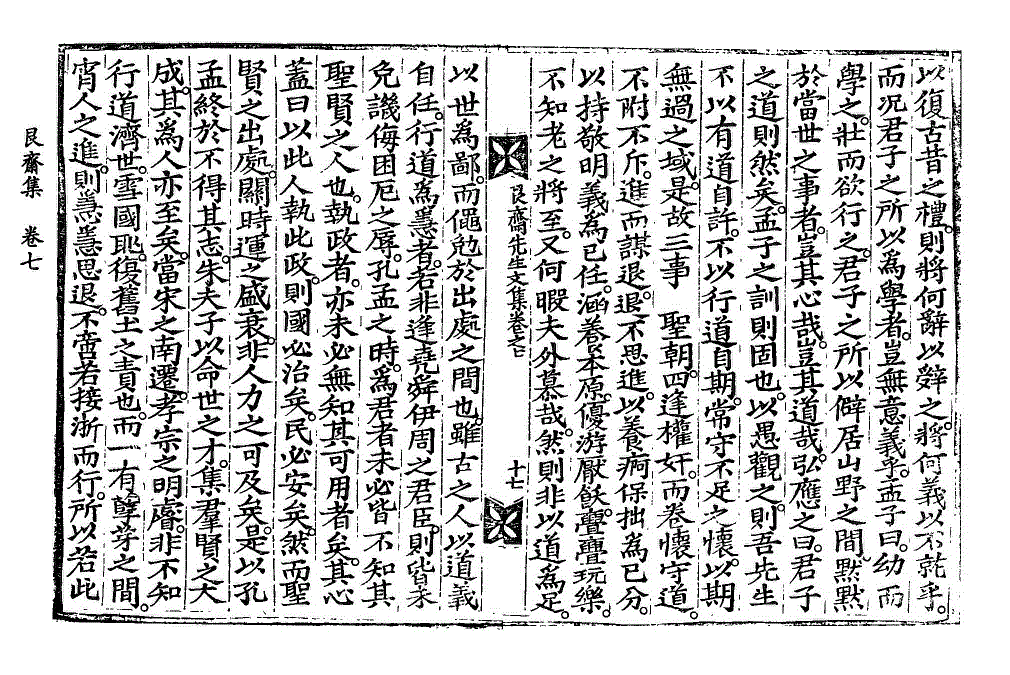 以复古昔之礼。则将何辞以辞之。将何义以不就乎。而况君子之所以为学者。岂无意义乎。孟子曰。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君子之所以僻居出野之间。默默于当世之事者。岂其心哉。岂其道哉。弘应之曰。君子之道则然矣。孟子之训则固也。以愚观之。则吾先生不以有道自许。不以行道自期。常守不足之怀。以期无过之域。是故三事圣朝。四逢权奸。而卷怀守道。不附不斥。进而谋退。退不思进。以养痾保拙为己分。以持敬明义为己任。涵养本原。优游厌饫。亹亹玩乐。不知老之将至。又何暇夫外慕哉。然则非以道为足。以世为鄙。而僶勉于出处之间也。虽古之人以道义自任。行道为急者。若非逢尧舜伊周之君臣。则皆未免讥侮困厄之辱。孔孟之时。为君者未必皆不知其圣贤之人也。执政者。亦未必无知其可用者矣。其心盖曰以此人执此政。则国必治矣。民必安矣。然而圣贤之出处。关时运之盛衰。非人力之可及矣。是以孔孟终于不得其志。朱夫子以命世之才。集群贤之大成。其为人亦至矣。当宋之南迁。孝宗之明睿。非不知行道济世。雪国耻。复旧土之责也。而一有孽芽之间。宵人之进。则急急思退。不啻若接淅而行。所以若此
以复古昔之礼。则将何辞以辞之。将何义以不就乎。而况君子之所以为学者。岂无意义乎。孟子曰。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君子之所以僻居出野之间。默默于当世之事者。岂其心哉。岂其道哉。弘应之曰。君子之道则然矣。孟子之训则固也。以愚观之。则吾先生不以有道自许。不以行道自期。常守不足之怀。以期无过之域。是故三事圣朝。四逢权奸。而卷怀守道。不附不斥。进而谋退。退不思进。以养痾保拙为己分。以持敬明义为己任。涵养本原。优游厌饫。亹亹玩乐。不知老之将至。又何暇夫外慕哉。然则非以道为足。以世为鄙。而僶勉于出处之间也。虽古之人以道义自任。行道为急者。若非逢尧舜伊周之君臣。则皆未免讥侮困厄之辱。孔孟之时。为君者未必皆不知其圣贤之人也。执政者。亦未必无知其可用者矣。其心盖曰以此人执此政。则国必治矣。民必安矣。然而圣贤之出处。关时运之盛衰。非人力之可及矣。是以孔孟终于不得其志。朱夫子以命世之才。集群贤之大成。其为人亦至矣。当宋之南迁。孝宗之明睿。非不知行道济世。雪国耻。复旧土之责也。而一有孽芽之间。宵人之进。则急急思退。不啻若接淅而行。所以若此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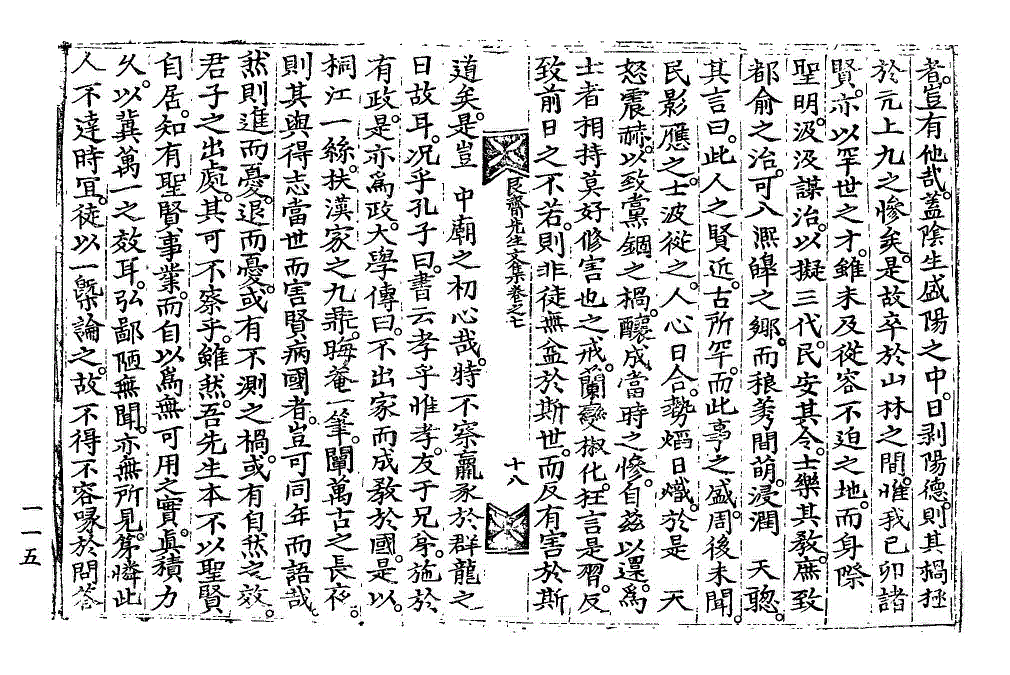 者。岂有他哉。盖阴生盛阳之中。日剥阳德。则其祸极于亢上九之惨矣。是故卒于山林之间。惟我己卯诸贤。亦以罕世之才。虽未及从容不迫之地。而身际圣明。汲汲谋治。以拟三代。民安其令。士乐其教。庶致都俞之治。可入熙皞之乡。而稂莠间萌。浸润天聪。其言曰。此人之贤近。古所罕。而此事之盛。周后未闻。民影应之。士波从之。人心日合。势焰日炽。于是天怒震赫。以致党锢之祸。酿成当时之惨。自玆以还。为士者相持莫好修害也之戒。兰变椒化。狂言是习。反致前日之不若。则非徒无益于斯世。而反有害于斯道矣。是岂中庙之初心哉。特不察羸豕于群龙之日故耳。况乎孔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大学传曰。不出家而成教于国。是以。桐江一丝。扶汉家之九鼎。晦庵一笔。阐万古之长夜。则其与得志当世而害贤病国者。岂可同年而语哉。然则进而忧。退而忧。或有不测之祸。或有自然之效。君子之出处。其可不察乎。虽然。吾先生本不以圣贤自居。知有圣贤事业。而自以为无可用之实。真积力久。以冀万一之效耳。弘鄙陋无闻。亦无所见。第怜此人不达时宜。从以一槩论之。故不得不容喙于问答
者。岂有他哉。盖阴生盛阳之中。日剥阳德。则其祸极于亢上九之惨矣。是故卒于山林之间。惟我己卯诸贤。亦以罕世之才。虽未及从容不迫之地。而身际圣明。汲汲谋治。以拟三代。民安其令。士乐其教。庶致都俞之治。可入熙皞之乡。而稂莠间萌。浸润天聪。其言曰。此人之贤近。古所罕。而此事之盛。周后未闻。民影应之。士波从之。人心日合。势焰日炽。于是天怒震赫。以致党锢之祸。酿成当时之惨。自玆以还。为士者相持莫好修害也之戒。兰变椒化。狂言是习。反致前日之不若。则非徒无益于斯世。而反有害于斯道矣。是岂中庙之初心哉。特不察羸豕于群龙之日故耳。况乎孔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大学传曰。不出家而成教于国。是以。桐江一丝。扶汉家之九鼎。晦庵一笔。阐万古之长夜。则其与得志当世而害贤病国者。岂可同年而语哉。然则进而忧。退而忧。或有不测之祸。或有自然之效。君子之出处。其可不察乎。虽然。吾先生本不以圣贤自居。知有圣贤事业。而自以为无可用之实。真积力久。以冀万一之效耳。弘鄙陋无闻。亦无所见。第怜此人不达时宜。从以一槩论之。故不得不容喙于问答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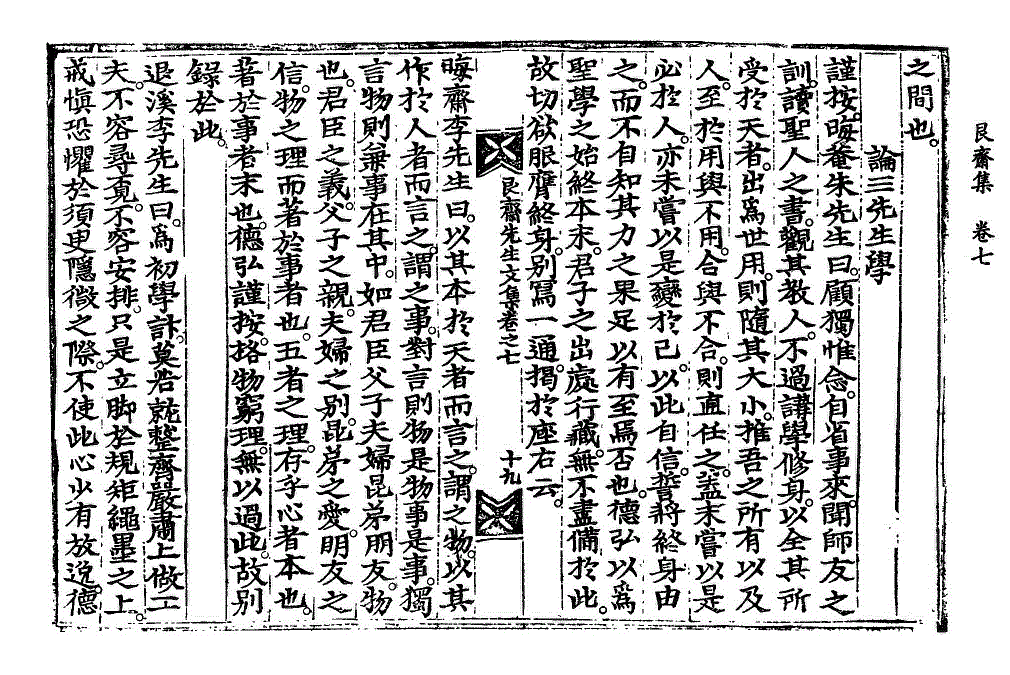 之间也。
之间也。论三先生学
谨按。晦庵朱先生曰。顾独惟念。自省事来。闻师友之训。读圣人之书。观其教人。不过讲学修身。以全其所受于天者。出为世用。则随其大小。推吾之所有以及人。至于用与不用。合与不合。则直任之。盖未尝以是必于人。亦未尝以是变于己。以此自信。誓将终身由之。而不自知其力之果足以有至焉否也。德弘以为圣学之始终本末。君子之出处行藏。无不尽备于此。故切欲服膺终身。别写一通。揭于座右云。
晦斋李先生曰。以其本于天者而言之。谓之物。以其作于人者而言之。谓之事。对言则物是物事是事。独言物则兼事在其中。如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物也。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昆弟之爱。朋友之信。物之理而著于事者也。五者之理。存乎心者本也。著于事者末也。德弘谨按。格物穷理。无以过此。故别录于此。
退溪李先生曰。为初学计。莫若就整齐严肃上做工夫。不容寻觅。不容安排。只是立脚于规矩绳墨之上。戒慎恐惧于须臾隐微之际。不使此心少有放逸。德
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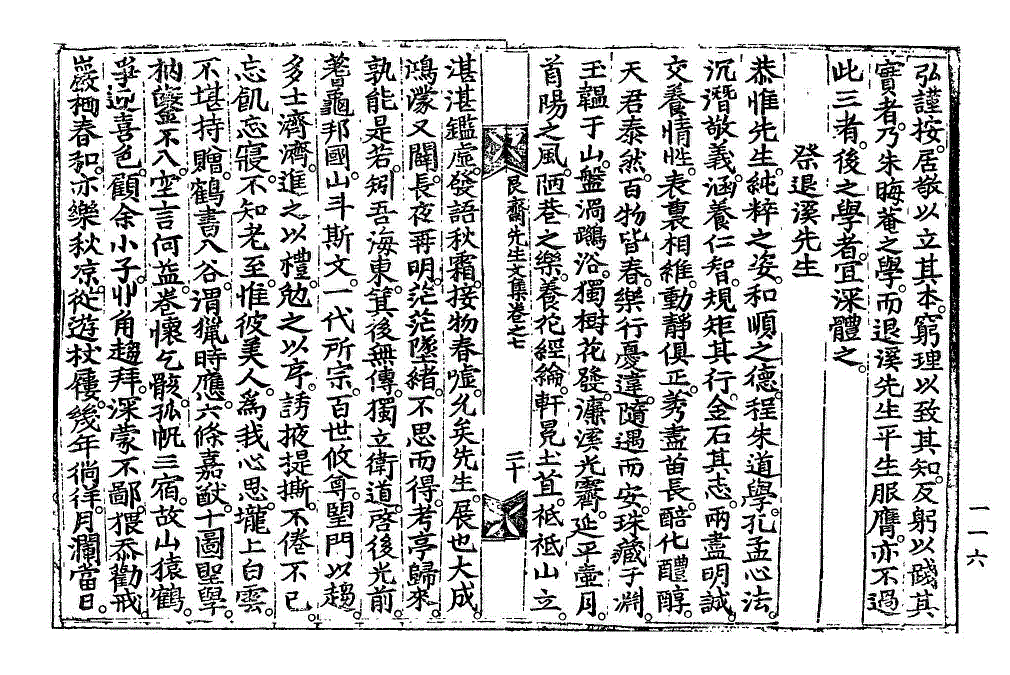 弘谨按。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者。乃朱晦庵之学。而退溪先生平生服膺。亦不过此三者。后之学者。宜深体之。
弘谨按。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者。乃朱晦庵之学。而退溪先生平生服膺。亦不过此三者。后之学者。宜深体之。祭退溪先生
恭惟先生。纯粹之姿。和顺之德。程朱道学。孔孟心法。沉潜敬义。涵养仁智。规矩其行。金石其志。两尽明诚。交养情性。表里相维。动静俱正。莠尽苗长。醅化醴醇。天君泰然。百物皆春。乐行忧违。随遇而安。珠藏于渊。玉韫于山。盘涡鹭浴。独树花发。濂溪光霁。延平壶月。首阳之风。陋巷之乐。养花经纶。轩冕土苴。祗祗山立。湛湛鉴虚。发语秋霜。接物春嘘。允矣先生。展也大成。鸿濛又辟。长夜再明。茫茫坠绪。不思而得。考亭归来。孰能是若。矧吾海东。箕后无传。独立卫道。启后光前。蓍龟邦国。山斗斯文。一代所宗。百世攸尊。望门以趋。多士济济。进之以礼。勉之以序。诱掖提撕。不倦不已。忘饥忘寝。不知老至。惟彼美人。为我心思。垄上白云。不堪持赠。鹤书入谷。渭猎时应。六条嘉猷。十图圣学。枘凿不入。空言何益。卷怀乞骸。孤帆三宿。故山猿鹤。争迎喜色。顾余小子。丱角趋拜。深蒙不鄙。猥忝劝戒。岩栖春和。亦乐秋凉。从游杖屦。几年徜徉。月澜当日。
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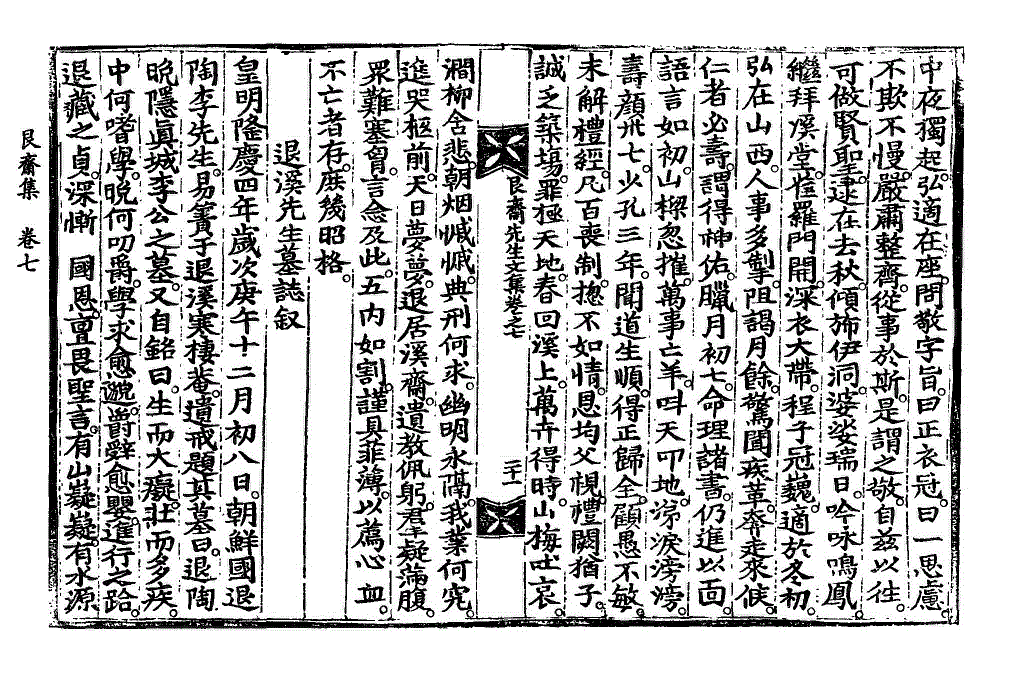 中夜独起。弘适在座。问敬字旨。曰正衣冠。曰一思虑。不欺不慢。严肃整齐。从事于斯。是谓之敬。自玆以往。可做贤圣。逮在去秋。倾旆伊洞。婆娑瑞日。吟咏鸣凤。继拜溪堂。崔罗门开。深衣大带。程子冠巍。适于冬初。弘在山西。人事多掣。阻谒月馀。惊闻病革。奔走来候。仁者必寿。谓得神佑。腊月初七。命理诸书。仍进以面。语言如初。山梁忽摧。万事亡羊。叫天叩地。涕泪滂滂。寿颜卅七。少孔三年。闻道生顺。得正归全。顾愚不敏。未解礼经。凡百丧制。揔不如情。恩均父视。礼阙犹子。诚乏筑场。罪极天地。春回溪上。万卉得时。山梅吐哀。涧柳含悲。朝烟戚戚。典刑何求。幽明永隔。我业何究。进哭柩前。天日梦梦。退居溪斋。遗教佩躬。群疑满腹。众难塞胸。言念及此。五内如割。谨具菲薄。以荐心血。不亡者存。庶几昭格。
中夜独起。弘适在座。问敬字旨。曰正衣冠。曰一思虑。不欺不慢。严肃整齐。从事于斯。是谓之敬。自玆以往。可做贤圣。逮在去秋。倾旆伊洞。婆娑瑞日。吟咏鸣凤。继拜溪堂。崔罗门开。深衣大带。程子冠巍。适于冬初。弘在山西。人事多掣。阻谒月馀。惊闻病革。奔走来候。仁者必寿。谓得神佑。腊月初七。命理诸书。仍进以面。语言如初。山梁忽摧。万事亡羊。叫天叩地。涕泪滂滂。寿颜卅七。少孔三年。闻道生顺。得正归全。顾愚不敏。未解礼经。凡百丧制。揔不如情。恩均父视。礼阙犹子。诚乏筑场。罪极天地。春回溪上。万卉得时。山梅吐哀。涧柳含悲。朝烟戚戚。典刑何求。幽明永隔。我业何究。进哭柩前。天日梦梦。退居溪斋。遗教佩躬。群疑满腹。众难塞胸。言念及此。五内如割。谨具菲薄。以荐心血。不亡者存。庶几昭格。退溪先生墓志叙
皇明隆庆四年岁次庚午十二月初八日。朝鲜国退陶李先生。易箦于退溪寒栖庵。遗戒题其墓曰。退陶晚隐真城李公之墓。又自铭曰。生而大痴。壮而多疾。中何嗜学。晚何叨爵。学求愈邈。爵辞愈婴。进行之跲。退藏之贞。深惭国恩。亶畏圣言。有山嶷嶷。有水源
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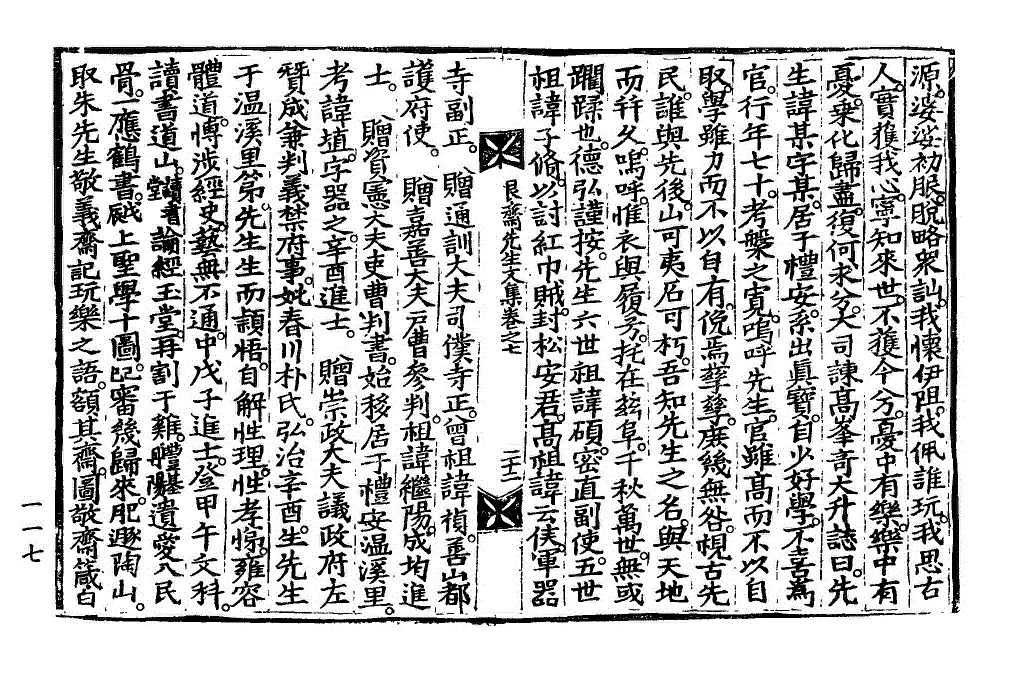 源。婆娑初服。脱略众讪。我怀伊阻。我佩谁玩。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宁知来世。不获今兮。忧中有乐。乐中有忧。乘化归尽。复何求兮。大司谏高峰奇大升志曰。先生讳某字某。居于礼安。系出真宝。自少好学。不喜为官。行年七十。考槃之宽。呜呼先生。官虽高而不以自取。举虽力而不以自有。俛焉孳孳。庶几无咎。视古先民。谁与先后。山可夷石可朽。吾知先生之名。与天地而并久。呜呼。惟衣与履兮。托在兹阜。千秋万世。无或躏蹂也。德弘谨按。先生六世祖讳硕。密直副使。五世祖讳子脩。以讨红巾贼。封松安君。高祖讳云侯。军器寺副正。赠通训大夫司仆寺正。曾祖讳祯。善山都护府使。赠嘉善大夫户曹参判。祖讳继阳。成均进士。赠资宪大夫吏曹判书。始移居于礼安温溪里。考讳埴。字器之。辛酉进士。赠崇政大夫议政府左赞成兼判义禁府事。妣春川朴氏。弘治辛酉。生先生于温溪里第。先生生而颖悟。自解性理。性孝悌。雍容体道。博涉经史。艺无不通。中戊子进士。登甲午文科。读书道山。(读书堂)论经玉堂。再割于鸡。(丰基丹阳)遗爱入民骨。一应鹤书。(戊辰)上圣学十图。(己巳)审几归来。肥遁陶山。取朱先生敬义斋记玩乐之语。额其斋。图敬斋箴,白
源。婆娑初服。脱略众讪。我怀伊阻。我佩谁玩。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宁知来世。不获今兮。忧中有乐。乐中有忧。乘化归尽。复何求兮。大司谏高峰奇大升志曰。先生讳某字某。居于礼安。系出真宝。自少好学。不喜为官。行年七十。考槃之宽。呜呼先生。官虽高而不以自取。举虽力而不以自有。俛焉孳孳。庶几无咎。视古先民。谁与先后。山可夷石可朽。吾知先生之名。与天地而并久。呜呼。惟衣与履兮。托在兹阜。千秋万世。无或躏蹂也。德弘谨按。先生六世祖讳硕。密直副使。五世祖讳子脩。以讨红巾贼。封松安君。高祖讳云侯。军器寺副正。赠通训大夫司仆寺正。曾祖讳祯。善山都护府使。赠嘉善大夫户曹参判。祖讳继阳。成均进士。赠资宪大夫吏曹判书。始移居于礼安温溪里。考讳埴。字器之。辛酉进士。赠崇政大夫议政府左赞成兼判义禁府事。妣春川朴氏。弘治辛酉。生先生于温溪里第。先生生而颖悟。自解性理。性孝悌。雍容体道。博涉经史。艺无不通。中戊子进士。登甲午文科。读书道山。(读书堂)论经玉堂。再割于鸡。(丰基丹阳)遗爱入民骨。一应鹤书。(戊辰)上圣学十图。(己巳)审几归来。肥遁陶山。取朱先生敬义斋记玩乐之语。额其斋。图敬斋箴,白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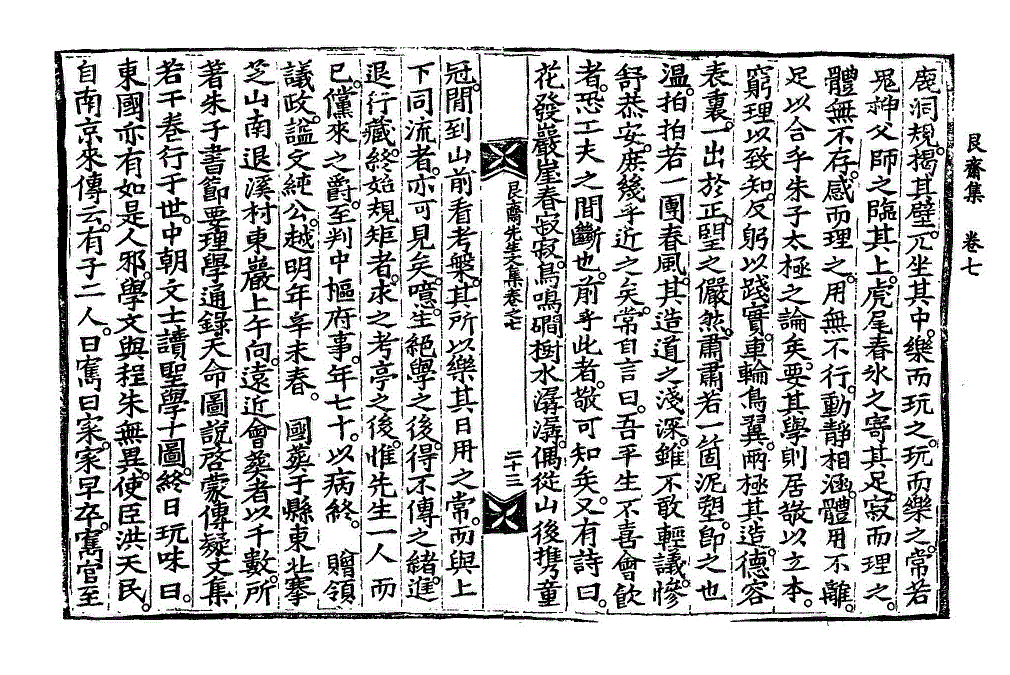 鹿洞规。揭其壁。兀坐其中。乐而玩之。玩而乐之。常若鬼神父师之临其上。虎尾春冰之寄其足。寂而理之。体无不存。感而理之。用无不行。动静相涵。体用不离。足以合乎朱子太极之论矣。要其学则居敬以立本。穷理以致知。反躬以践实。车轮鸟翼。两极其造。德容表里。一出于正。望之俨然。肃肃若一个泥塑。即之也温。拍拍若一团春风。其造道之浅深。虽不敢轻议。惨舒恭安。庶几乎近之矣。常自言曰。吾平生不喜会饮者。恐工夫之间断也。前乎此者。敬可知矣。又有诗曰。花发岩崖春寂寂。鸟鸣涧树水潺潺。偶从山后携童冠。閒到山前看考槃。其所以乐其日用之常。而与上下同流者。亦可见矣。噫。生绝学之后。得不传之绪。进退行藏。终始规矩者。求之考亭之后。惟先生一人而已。傥来之爵。至判中枢府事。年七十。以病终。赠领议政。谥文纯公。越明年辛未春。国葬于县东北搴芝山南退溪村东岩上午向。远近会葬者以千数。所著朱子书节要理学通录天命图说启蒙传疑,文集若干卷行于世。中朝文士读圣学十图。终日玩味曰。东国亦有如是人邪。学文与程朱无异。使臣洪天民。自南京来传云。有子二人。曰寯曰寀。寀早卒。寯官至
鹿洞规。揭其壁。兀坐其中。乐而玩之。玩而乐之。常若鬼神父师之临其上。虎尾春冰之寄其足。寂而理之。体无不存。感而理之。用无不行。动静相涵。体用不离。足以合乎朱子太极之论矣。要其学则居敬以立本。穷理以致知。反躬以践实。车轮鸟翼。两极其造。德容表里。一出于正。望之俨然。肃肃若一个泥塑。即之也温。拍拍若一团春风。其造道之浅深。虽不敢轻议。惨舒恭安。庶几乎近之矣。常自言曰。吾平生不喜会饮者。恐工夫之间断也。前乎此者。敬可知矣。又有诗曰。花发岩崖春寂寂。鸟鸣涧树水潺潺。偶从山后携童冠。閒到山前看考槃。其所以乐其日用之常。而与上下同流者。亦可见矣。噫。生绝学之后。得不传之绪。进退行藏。终始规矩者。求之考亭之后。惟先生一人而已。傥来之爵。至判中枢府事。年七十。以病终。赠领议政。谥文纯公。越明年辛未春。国葬于县东北搴芝山南退溪村东岩上午向。远近会葬者以千数。所著朱子书节要理学通录天命图说启蒙传疑,文集若干卷行于世。中朝文士读圣学十图。终日玩味曰。东国亦有如是人邪。学文与程朱无异。使臣洪天民。自南京来传云。有子二人。曰寯曰寀。寀早卒。寯官至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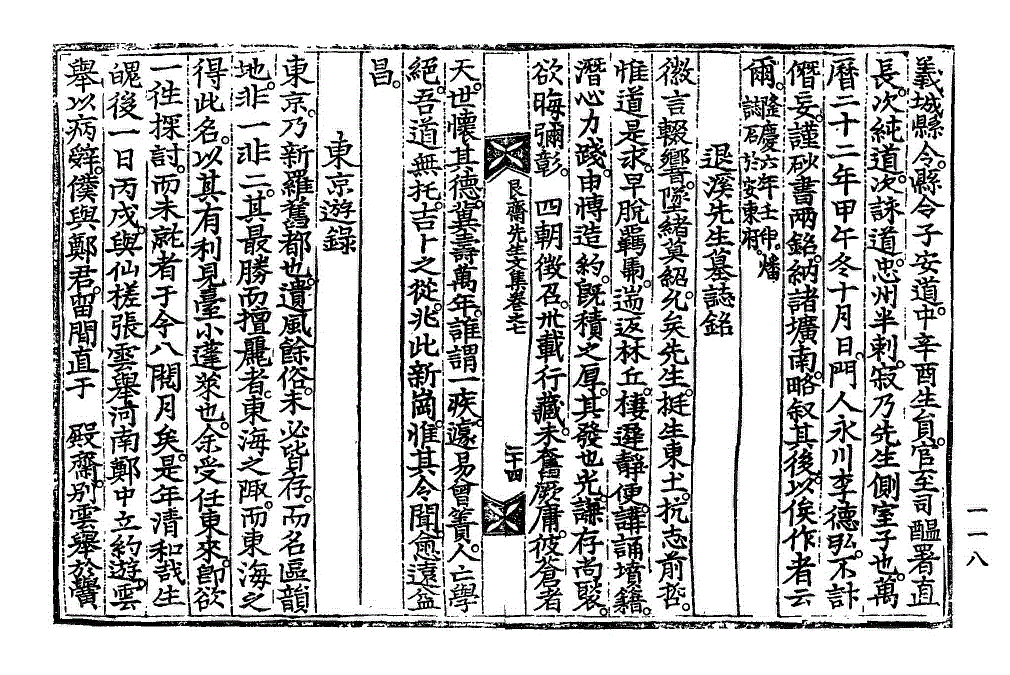 义城县令。县令子安道。中辛酉生员。官至司酝署直长。次纯道。次咏道。忠州半刺。寂乃先生侧室子也。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冬十月日。门人永川李德弘。不计僭妄。谨砂书两铭。纳诸圹南。略叙其后。以俟作者云尔。(隆庆六年壬申。燔志石于安东府。)
义城县令。县令子安道。中辛酉生员。官至司酝署直长。次纯道。次咏道。忠州半刺。寂乃先生侧室子也。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冬十月日。门人永川李德弘。不计僭妄。谨砂书两铭。纳诸圹南。略叙其后。以俟作者云尔。(隆庆六年壬申。燔志石于安东府。)退溪先生墓志铭
徽言辍响。坠绪莫绍。允矣先生。挺生东土。抗志前哲。惟道是求。早脱羁絷。遄返林丘。栖迟静便。讲诵坟籍。潜心力践。由博造约。既积之厚。其发也光。谦存尚褧。欲晦弥彰。四朝徵召。卅载行藏。未奋厥庸。彼苍者天。世怀其德。冀寿万年。谁谓一疾。遽易曾箦。人亡学绝。吾道无托。吉卜之从。兆此新岗。惟其令闻。愈远益昌。
东京游录
东京。乃新罗旧都也。遗风馀俗。未必皆存。而名区韵地。非一非二。其最胜而擅丽者。东海之陬。而东海之得此名。以其有利见台小蓬莱也。余受任东来。即欲一往探讨而未就者于今八阅月矣。是年清和哉生魄后一日丙戌。与仙槎张云举河南郑中立约游。云举以病辞。仆与郑君。留闻直于殿斋。别云举于黉
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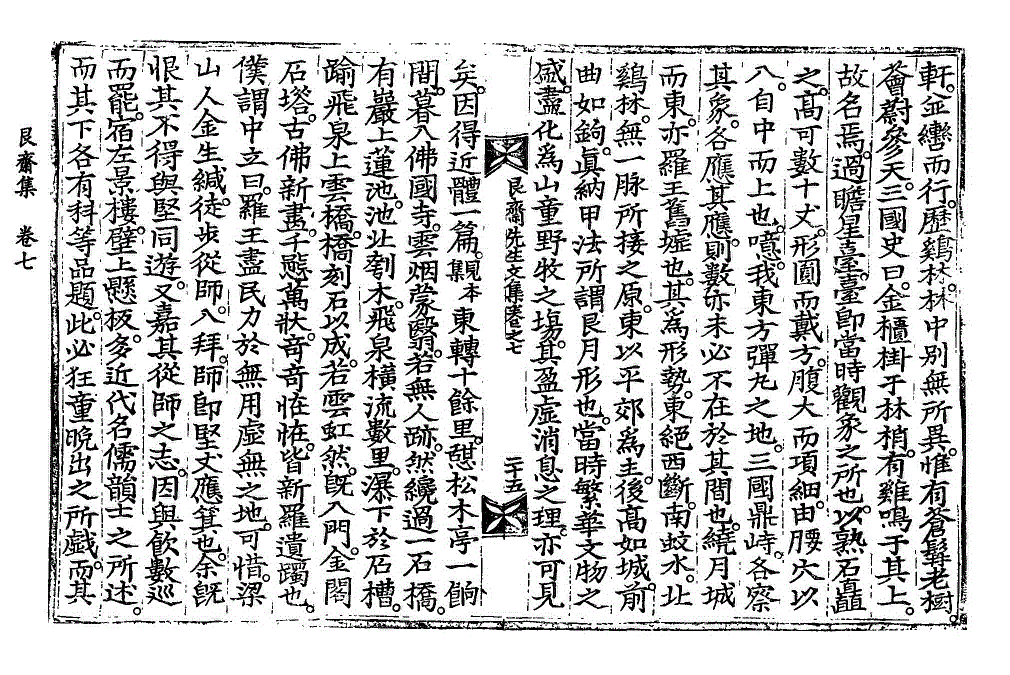 轩。并辔而行。历鸡林。林中别无所异。惟有苍髯老树。荟蔚参天。三国史曰。金匮挂于林梢。有鸡鸣于其上。故名焉。过瞻星台。台即当时观象之所也。以熟石矗之。高可数十丈。形圆而戴方。腹大而项细。由腰穴以入。自中而上也。噫。我东方弹丸之地。三国鼎峙。各察其象。各应其应。则数亦未必不在于其间也。绕月城而东。亦罗王旧墟也。其为形势。东绝西断。南蚊水。北鸡林。无一咏所接之原。东以平郊为主。后高如城。前曲如钩。真纳甲法所谓艮月形也。当时繁华文物之盛。尽化为山童野牧之场。其盈虚消息之理。亦可见矣。因得近体一篇。(见本集)东转十馀里。憩松木亭一饷间。暮入佛国寺。云烟蒙翳。若无人迹。然才过一石桥。有岩上莲池。池北刳木。飞泉横流数里。瀑下于石槽。踰飞泉上云桥。桥刻石以成。若云虹然。既入门。金阁石塔。古佛新画。千态万状。奇奇怪怪。皆新罗遗躅也。仆谓中立曰。罗王尽民力于无用虚无之地。可惜。梁山人金生缄。徒步从师。入拜。师即坚丈应箕也。余既恨其不得与坚同游。又嘉其从师之志。因与饮数巡而罢。宿左景楼。壁上悬板。多近代名儒韵士之所述。而其下各有科等品题。此必狂童晚出之所戏。而其
轩。并辔而行。历鸡林。林中别无所异。惟有苍髯老树。荟蔚参天。三国史曰。金匮挂于林梢。有鸡鸣于其上。故名焉。过瞻星台。台即当时观象之所也。以熟石矗之。高可数十丈。形圆而戴方。腹大而项细。由腰穴以入。自中而上也。噫。我东方弹丸之地。三国鼎峙。各察其象。各应其应。则数亦未必不在于其间也。绕月城而东。亦罗王旧墟也。其为形势。东绝西断。南蚊水。北鸡林。无一咏所接之原。东以平郊为主。后高如城。前曲如钩。真纳甲法所谓艮月形也。当时繁华文物之盛。尽化为山童野牧之场。其盈虚消息之理。亦可见矣。因得近体一篇。(见本集)东转十馀里。憩松木亭一饷间。暮入佛国寺。云烟蒙翳。若无人迹。然才过一石桥。有岩上莲池。池北刳木。飞泉横流数里。瀑下于石槽。踰飞泉上云桥。桥刻石以成。若云虹然。既入门。金阁石塔。古佛新画。千态万状。奇奇怪怪。皆新罗遗躅也。仆谓中立曰。罗王尽民力于无用虚无之地。可惜。梁山人金生缄。徒步从师。入拜。师即坚丈应箕也。余既恨其不得与坚同游。又嘉其从师之志。因与饮数巡而罢。宿左景楼。壁上悬板。多近代名儒韵士之所述。而其下各有科等品题。此必狂童晚出之所戏。而其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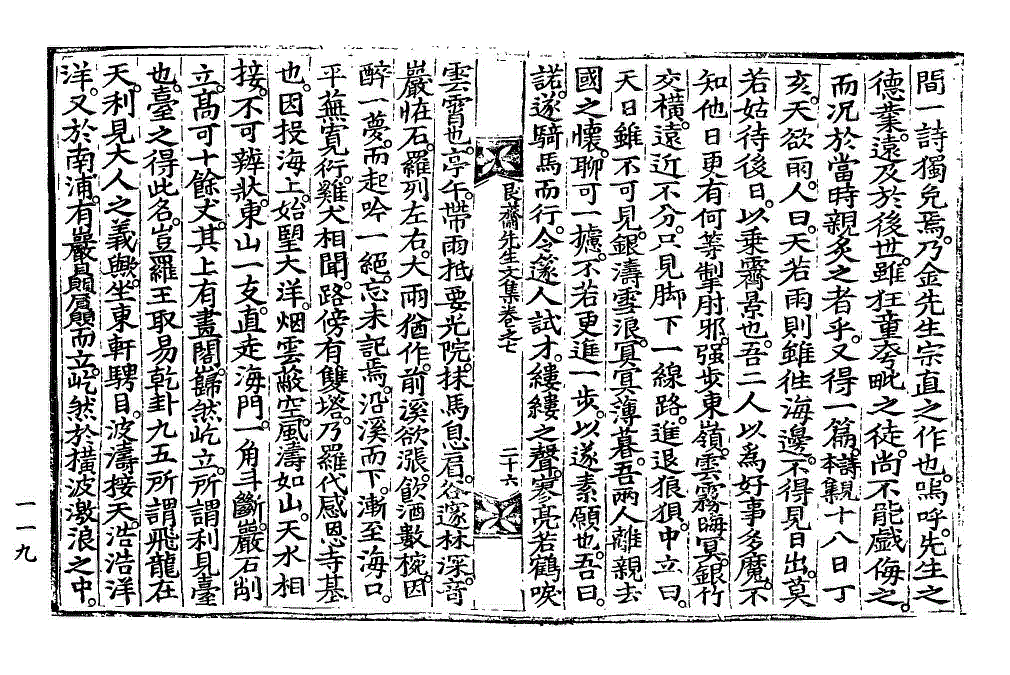 间一诗独免焉。乃金先生宗直之作也。呜呼。先生之德业。远及于后世。虽狂童夸毗之徒。尚不能戏侮之。而况于当时亲炙之者乎。又得一篇。(诗见本集)十八日丁亥。天欲雨。人曰。天若雨则虽往海边。不得见日出。莫若姑待后日。以乘霁景也。吾二人以为好事多魔。不知他日更有何等掣肘邪。强步东岭。云雾晦冥。银竹交横。远近不分。只见脚下一线路。进退狼狈。中立曰。天日虽不可见。银涛雪浪。冥冥薄暮。吾两人离亲去国之怀。聊可一摅。不若更进一步。以遂素愿也。吾曰。诺。遂骑马而行。令篴人试才。缕缕之声。寥亮若鹤唳云霄也。亭午。带雨抵要光院。抹马息肩。谷邃林深。奇岩怪石。罗列左右。大雨犹作。前溪欲涨。饮酒数碗。因醉一梦。而起吟一绝。忘未记焉。沿溪而下。渐至海口。平芜宽衍。鸡犬相闻。路傍有双塔。乃罗代感恩寺基也。因投海上。始望大洋。烟云蔽空。风涛如山。天水相接。不可辨状。东山一支。直走海门。一角斗断。岩石削立。高可十馀丈。其上有画阁。岿然屹立。所谓利见台也。台之得此名。岂罗王取易乾封九五所谓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之义欤。坐东轩骋目。波涛接天。浩浩洋洋。又于南浦。有岩赑屃而立。屹然于横波激浪之中。
间一诗独免焉。乃金先生宗直之作也。呜呼。先生之德业。远及于后世。虽狂童夸毗之徒。尚不能戏侮之。而况于当时亲炙之者乎。又得一篇。(诗见本集)十八日丁亥。天欲雨。人曰。天若雨则虽往海边。不得见日出。莫若姑待后日。以乘霁景也。吾二人以为好事多魔。不知他日更有何等掣肘邪。强步东岭。云雾晦冥。银竹交横。远近不分。只见脚下一线路。进退狼狈。中立曰。天日虽不可见。银涛雪浪。冥冥薄暮。吾两人离亲去国之怀。聊可一摅。不若更进一步。以遂素愿也。吾曰。诺。遂骑马而行。令篴人试才。缕缕之声。寥亮若鹤唳云霄也。亭午。带雨抵要光院。抹马息肩。谷邃林深。奇岩怪石。罗列左右。大雨犹作。前溪欲涨。饮酒数碗。因醉一梦。而起吟一绝。忘未记焉。沿溪而下。渐至海口。平芜宽衍。鸡犬相闻。路傍有双塔。乃罗代感恩寺基也。因投海上。始望大洋。烟云蔽空。风涛如山。天水相接。不可辨状。东山一支。直走海门。一角斗断。岩石削立。高可十馀丈。其上有画阁。岿然屹立。所谓利见台也。台之得此名。岂罗王取易乾封九五所谓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之义欤。坐东轩骋目。波涛接天。浩浩洋洋。又于南浦。有岩赑屃而立。屹然于横波激浪之中。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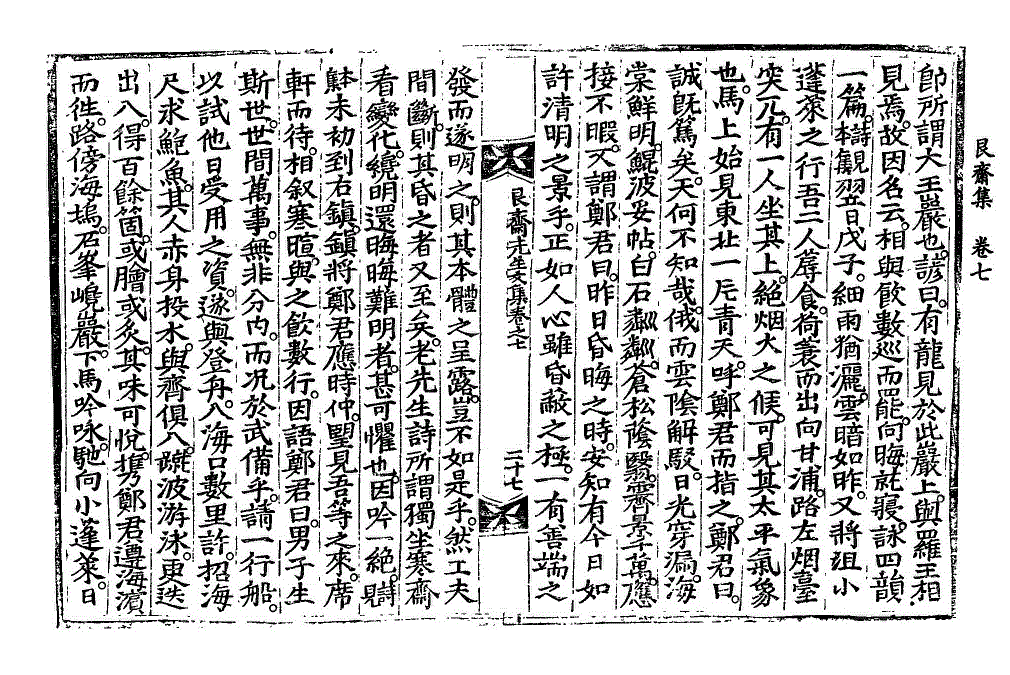 即所谓大王岩也。谚曰。有龙见于此岩上。与罗王相见焉。故因名云。相与饮数巡而罢。向晦就寝。咏四韵一篇。(诗见本集)翌日戊子。细雨犹洒。云暗如昨。又将沮小蓬莱之行吾二人蓐食。荷蓑而出向甘浦。路左烟台突兀。有一人坐其上。绝烟火之候。可见其太平气象也。马上始见东北一片青天。呼郑君而指之。郑君曰。诚既笃矣。天何不知哉。俄而云阴解驳。日光穿漏。海棠鲜明。鲲波妥帖。白石粼粼。苍松荫翳。霁景千万。应接不暇。又谓郑君曰。昨日昏晦之时。安知有今日如许清明之景乎。正如人心虽昏蔽之极。一有善端之发而遂明之。则其本体之呈露。岂不如是乎。然工夫间断。则其昏之者又至矣。老先生诗所谓独坐寒斋看变化。才明还晦晦难明者。甚可惧也。因吟一绝。(诗见本集)未初到右镇。镇将郑君应时仲。望见吾等之来。席轩而待。相叙寒暄。与之饮数行。因语郑君曰。男子生斯世。世间万事。无非分内。而况于武备乎。请一行船。以试他日受用之资。遂与登舟。入海口数里许。招海尺求鲍鱼。其人赤身投水。与齐俱入。蹴波游泳。更迭出入。得百馀个。或脍或炙。其味可悦。携郑君遵海滨而往。路傍海坞。石峰巉岩。下马吟咏。驰向小蓬莱。日
即所谓大王岩也。谚曰。有龙见于此岩上。与罗王相见焉。故因名云。相与饮数巡而罢。向晦就寝。咏四韵一篇。(诗见本集)翌日戊子。细雨犹洒。云暗如昨。又将沮小蓬莱之行吾二人蓐食。荷蓑而出向甘浦。路左烟台突兀。有一人坐其上。绝烟火之候。可见其太平气象也。马上始见东北一片青天。呼郑君而指之。郑君曰。诚既笃矣。天何不知哉。俄而云阴解驳。日光穿漏。海棠鲜明。鲲波妥帖。白石粼粼。苍松荫翳。霁景千万。应接不暇。又谓郑君曰。昨日昏晦之时。安知有今日如许清明之景乎。正如人心虽昏蔽之极。一有善端之发而遂明之。则其本体之呈露。岂不如是乎。然工夫间断。则其昏之者又至矣。老先生诗所谓独坐寒斋看变化。才明还晦晦难明者。甚可惧也。因吟一绝。(诗见本集)未初到右镇。镇将郑君应时仲。望见吾等之来。席轩而待。相叙寒暄。与之饮数行。因语郑君曰。男子生斯世。世间万事。无非分内。而况于武备乎。请一行船。以试他日受用之资。遂与登舟。入海口数里许。招海尺求鲍鱼。其人赤身投水。与齐俱入。蹴波游泳。更迭出入。得百馀个。或脍或炙。其味可悦。携郑君遵海滨而往。路傍海坞。石峰巉岩。下马吟咏。驰向小蓬莱。日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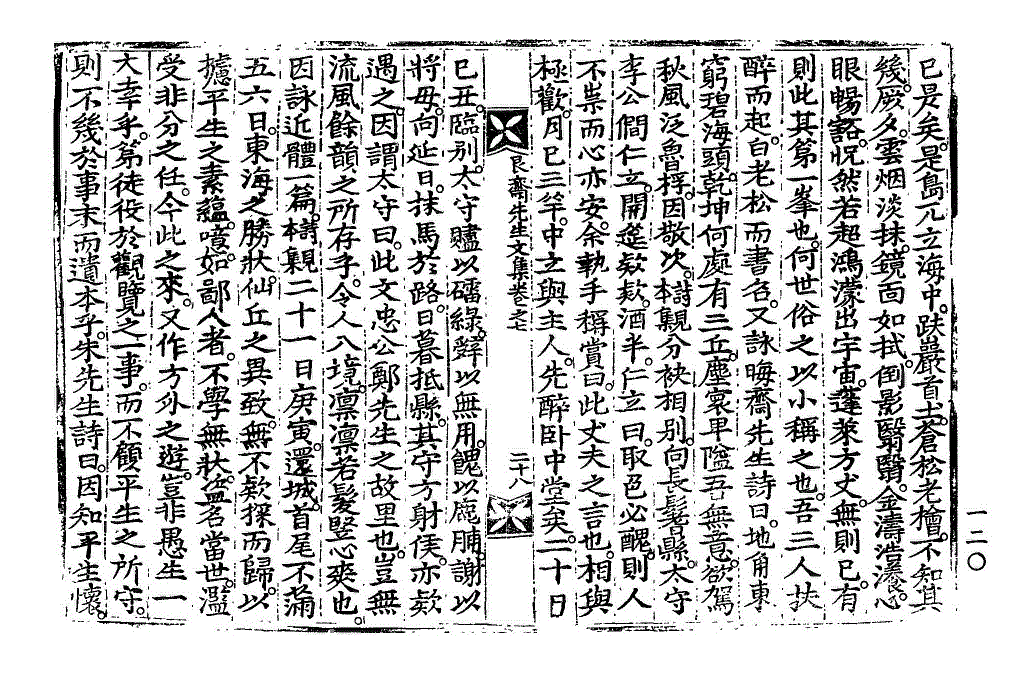 已昃矣。是岛兀立海中。趺岩首土。苍松老桧。不知其几。厥夕。云烟淡抹。镜面如拭。倒影翳翳。金涛浩瀁。心眼畅豁。恍然若超鸿濛出宇宙。蓬莱方丈。无则已。有则此其第一峰也。何世俗之以小称之也。吾三人扶醉而起。白老松而书名。又咏晦斋先生诗曰。地角东穷碧海头。乾坤何处有三丘。尘寰卑隘吾无意。欲驾秋风泛鲁桴。因敬次。(诗见本集)分袂相别。向长鬐县。太守李公僩仁立。开筵款款。酒半。仁立曰。取色必丑。则人不祟而心亦安。余执手称赏曰。此丈夫之言也。相与极欢。月已三竿。中立与主人。先醉卧中堂矣。二十日己丑。临别。太守赆以礌绿。辞以无用。馈以鹿脯。谢以将毋。向延日。抹马于路。日暮抵县。其守方射侯。亦款遇之。因谓太守曰。此文忠公郑先生之故里也。岂无流风馀韵之所存乎。令人入境。凛凛若发竖心爽也。因咏近体一篇。(诗见本集)二十一日庚寅。还城。首尾不满五六日。东海之胜状。仙丘之异致。无不款探而归。以摅平生之素蕴。噫。如鄙人者。不学无状。盗名当世。滥受非分之任。今此之来。又作方外之游。岂非愚生一大幸乎。第徒役于观览之一事。而不顾平生之所守。则不几于事末而遗本乎。朱先生诗曰。因知平生怀。
已昃矣。是岛兀立海中。趺岩首土。苍松老桧。不知其几。厥夕。云烟淡抹。镜面如拭。倒影翳翳。金涛浩瀁。心眼畅豁。恍然若超鸿濛出宇宙。蓬莱方丈。无则已。有则此其第一峰也。何世俗之以小称之也。吾三人扶醉而起。白老松而书名。又咏晦斋先生诗曰。地角东穷碧海头。乾坤何处有三丘。尘寰卑隘吾无意。欲驾秋风泛鲁桴。因敬次。(诗见本集)分袂相别。向长鬐县。太守李公僩仁立。开筵款款。酒半。仁立曰。取色必丑。则人不祟而心亦安。余执手称赏曰。此丈夫之言也。相与极欢。月已三竿。中立与主人。先醉卧中堂矣。二十日己丑。临别。太守赆以礌绿。辞以无用。馈以鹿脯。谢以将毋。向延日。抹马于路。日暮抵县。其守方射侯。亦款遇之。因谓太守曰。此文忠公郑先生之故里也。岂无流风馀韵之所存乎。令人入境。凛凛若发竖心爽也。因咏近体一篇。(诗见本集)二十一日庚寅。还城。首尾不满五六日。东海之胜状。仙丘之异致。无不款探而归。以摅平生之素蕴。噫。如鄙人者。不学无状。盗名当世。滥受非分之任。今此之来。又作方外之游。岂非愚生一大幸乎。第徒役于观览之一事。而不顾平生之所守。则不几于事末而遗本乎。朱先生诗曰。因知平生怀。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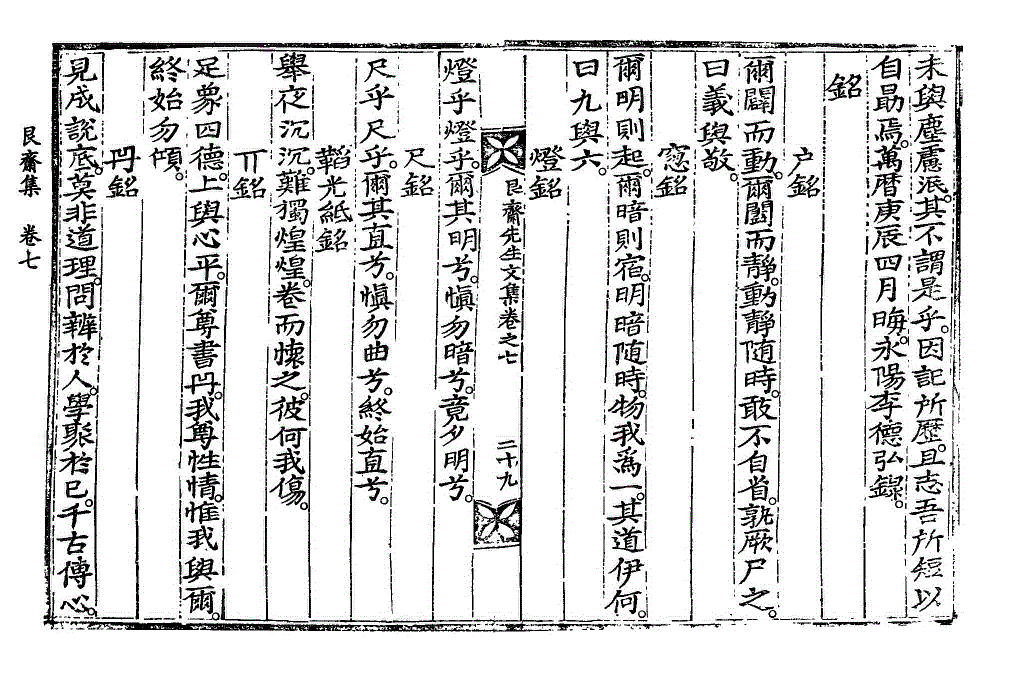 未与尘虑泯。其不谓是乎。因记所历。且志吾所短以自勖焉。万历庚辰四月晦。永阳李德弘录。
未与尘虑泯。其不谓是乎。因记所历。且志吾所短以自勖焉。万历庚辰四月晦。永阳李德弘录。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铭
户铭
尔辟而动。尔阖而静。动静随时。敢不自省。孰厥尸之。曰义与敬。
窗铭
尔明则起。尔暗则宿。明暗随时。物我为一。其道伊何。曰九与六。
灯铭
灯乎灯乎。尔其明兮。慎勿暗兮。竟夕明兮。
尺铭
尺乎尺乎。尔其直兮。慎勿曲兮。终始直兮。
韬光纸铭
举夜沉沉。难独煌煌。卷而怀之。彼何我伤。
丌铭
足象四德。上与心平。尔尊书册。我尊性情。惟我与尔。终始勿倾。
册铭
见成说底。莫非道理。问辨于人。学聚于己。千古传心。
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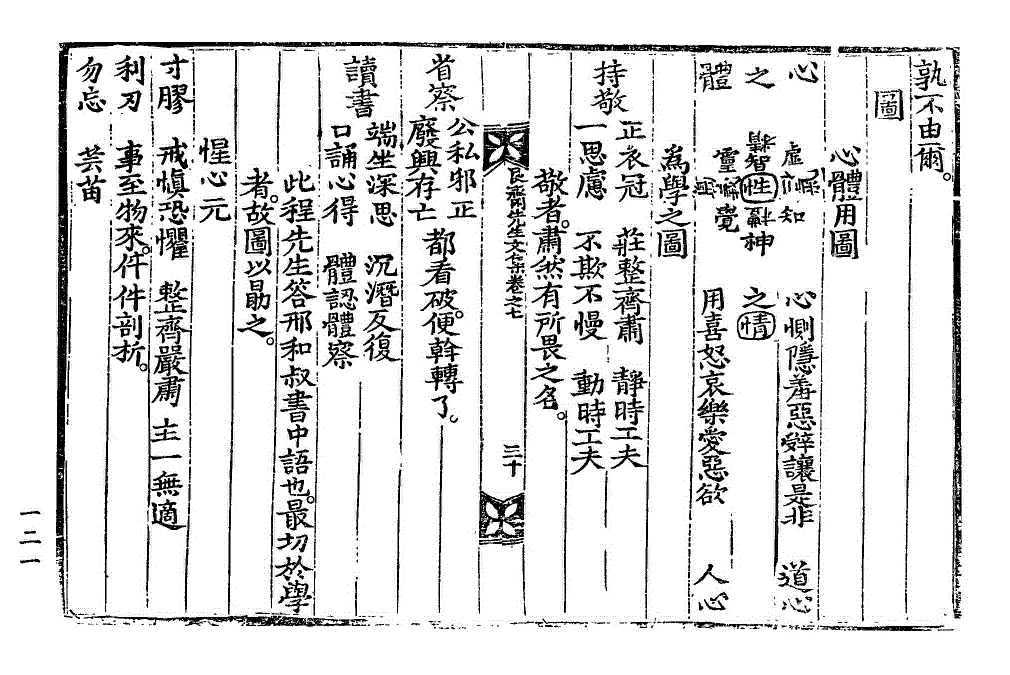 孰不由尔。
孰不由尔。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图
心体用图
삽화 새창열기
为学之图
持敬正衣冠庄整齐肃静时工夫
一思虑不欺不慢动时工夫
敬者肃然有所畏之名
省察公私邪正都看破便斡转了
废兴存亡
读书端坐深思沉潜反复
口诵心得体认体察
此程先生答邢和叔书中语也。最切于学者。故图以勖之。
惺心元
寸胶戒慎恐惧整齐严肃主一无适
利刃事至物来 件件剖析
勿忘芸苗
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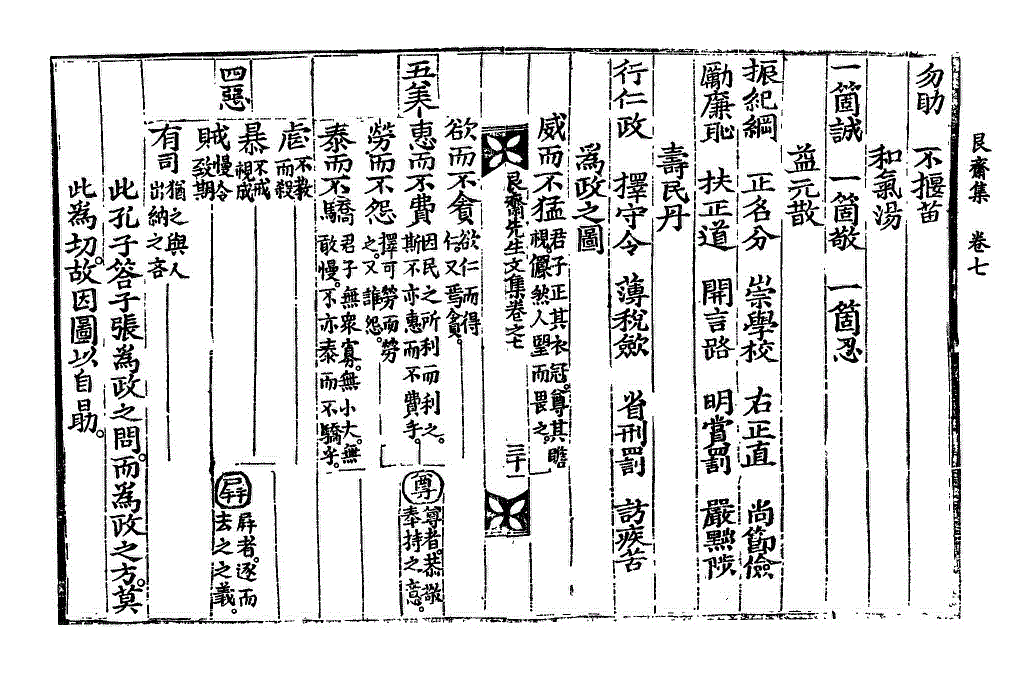 勿助不揠苗
勿助不揠苗和气汤
一个诚。一个敬。一个忍。
益元散
振纪纲。正名分。崇学校。右正直。尚节俭。励廉耻。扶正道。开言路。明赏罚。严黜陟。
寿民丹
行仁政。择守令。薄税敛。省刑罚。访疾苦。
为政之图
五美威而不猛(-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 -)
欲而不贪(- 欲仁而得仁。又焉贪。 -)
惠而不费(-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手。 -)
劳而不怨(- 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 -)
泰而不骄(- 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不亦泰而不骄乎。 -)
四恶虐(- 不教而杀 -)
暴(- 不戒视成 -)
贼(- 慢令致期 -)
有司(- 犹之与人出纳之吝 -)
此孔子答子张为政之问。而为政之方。莫此为切。故因图以自勖。
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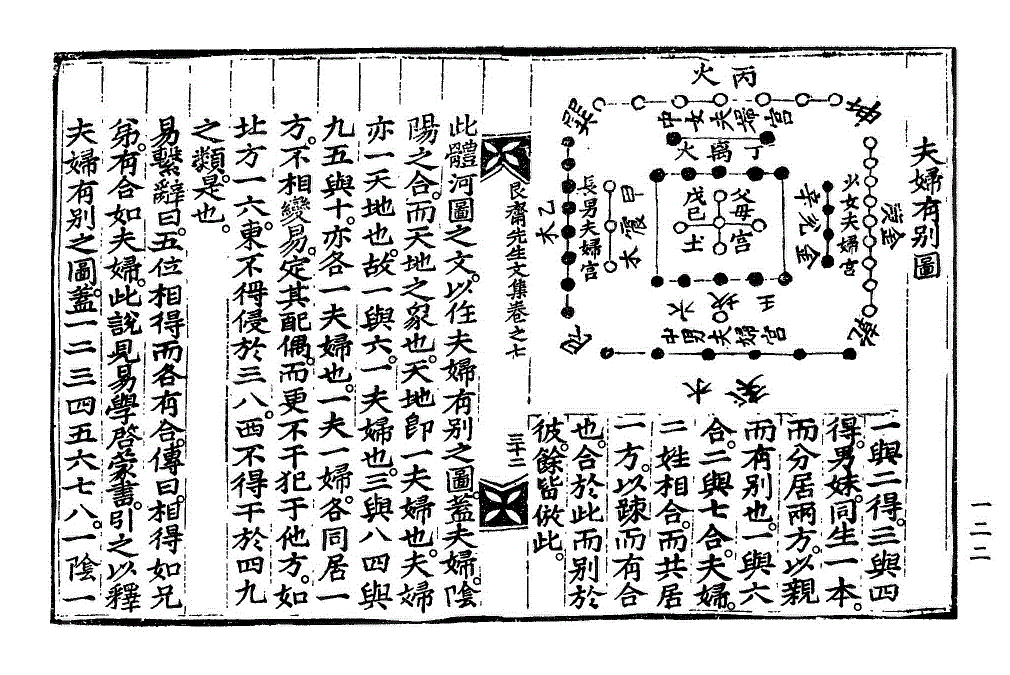 夫妇有别图
夫妇有别图삽화 새창열기
一与二得。三与四得。男妹。同生一本。而分居两方。以亲而有别也。一与六合。二与七合。夫妇。二姓相合。而共居一方。以疏而有合也。合于此而别于彼。馀皆仿此。
此体河图之文。以作夫妇有别之图。盖夫妇。阴阳之合。而天地之象也。天地即一夫妇也。夫妇亦一天地也。故一与六。一夫妇也。三与八四与九五与十。亦各一夫妇也。一夫一妇。各同居一方。不相变易。定其配偶。而更不干犯于他方。如北方一六。东不得侵于三八。西不得干于四九之类。是也。
易系辞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传曰。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妇。此说见易学启蒙书。引之以释夫妇有别之图。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阴一
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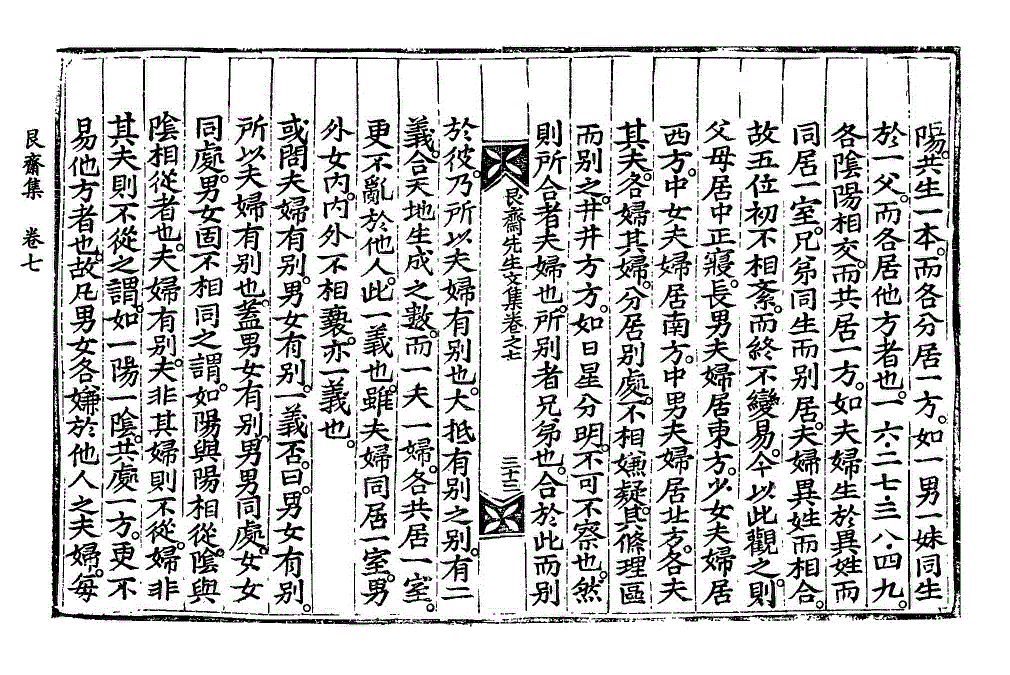 阳。共生一本。而各分居一方。如一男一妹同生于一父。而各居他方者也。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各阴阳相交。而共居一方。如夫妇生于异姓而同居一室。兄弟同生而别居。夫妇异姓而相合。故五位初不相紊。而终不变易。今以此观之。则父母居中正寝。长男夫妇居东方。少女夫妇居西方。中女夫妇居南方。中男夫妇居北方。各夫其夫。各妇其妇。分居别处。不相嫌疑。其条理区而别之。井井方方。如日星分明。不可不察也。然则所合者夫妇也。所别者兄弟也。合于此而别于彼。乃所以夫妇有别也。大抵有别之别。有二义。合天地生成之数。而一夫一妇。各共居一室。更不乱于他人。此一义也。虽夫妇同居一室。男外女内。内外不相亵。亦一义也。
阳。共生一本。而各分居一方。如一男一妹同生于一父。而各居他方者也。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各阴阳相交。而共居一方。如夫妇生于异姓而同居一室。兄弟同生而别居。夫妇异姓而相合。故五位初不相紊。而终不变易。今以此观之。则父母居中正寝。长男夫妇居东方。少女夫妇居西方。中女夫妇居南方。中男夫妇居北方。各夫其夫。各妇其妇。分居别处。不相嫌疑。其条理区而别之。井井方方。如日星分明。不可不察也。然则所合者夫妇也。所别者兄弟也。合于此而别于彼。乃所以夫妇有别也。大抵有别之别。有二义。合天地生成之数。而一夫一妇。各共居一室。更不乱于他人。此一义也。虽夫妇同居一室。男外女内。内外不相亵。亦一义也。或问夫妇有别。男女有别。一义否。曰。男女有别。所以夫妇有别也。盖男女有别。男男同处。女女同处。男女固不相同之谓。如阳与阳相从。阴与阴相从者也。夫妇有别。夫非其妇则不从。妇非其夫则不从之谓。如一阳一阴。共处一方。更不易他方者也。故凡男女各嫌于他人之夫妇。每
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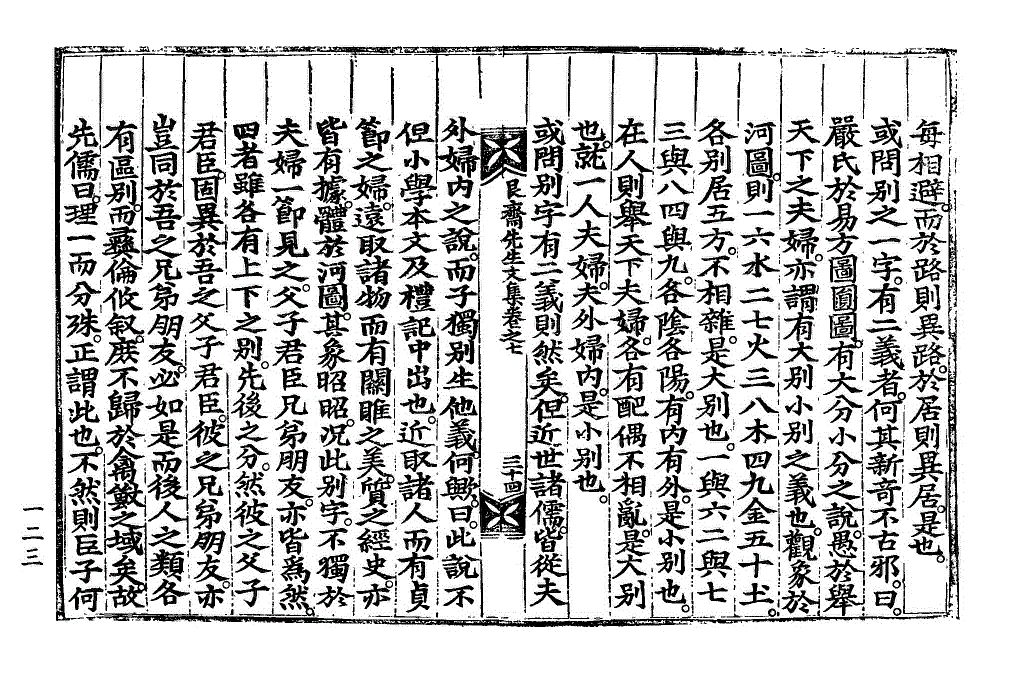 每相避。而于路则异路。于居则异居。是也。或问别之一字。有二义者。何其新奇不古邪。曰。严氏于易方图圆图。有大分小分之说。愚于举天下之夫妇。亦谓有大别小别之义也。观象于河图。则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十土。各别居五方。不相杂。是大别也。一与六二与七三与八四与九。各阴各阳。有内有外。是小别也。在人则举天下夫妇。各有配偶不相乱。是大别也。就一人夫妇。夫外妇内。是小别也。
每相避。而于路则异路。于居则异居。是也。或问别之一字。有二义者。何其新奇不古邪。曰。严氏于易方图圆图。有大分小分之说。愚于举天下之夫妇。亦谓有大别小别之义也。观象于河图。则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十土。各别居五方。不相杂。是大别也。一与六二与七三与八四与九。各阴各阳。有内有外。是小别也。在人则举天下夫妇。各有配偶不相乱。是大别也。就一人夫妇。夫外妇内。是小别也。或问别字有二义则然矣。但近世诸儒。皆从夫外妇内之说。而子独别生他义。何欤。曰。此说不但小学本文及礼记中出也。近取诸人而有贞节之妇。远取诸物而有关雎之美。质之经史。亦皆有据。体于河图。其象昭昭。况此别字。不独于夫妇一节见之。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亦皆为然。四者虽各有上下之别。先后之分。然彼之父子君臣。固异于吾之父子君臣。彼之兄弟朋友。亦岂同于吾之兄弟朋友。必如是而后人之类各有区别。而彝伦攸叙。庶不归于禽兽之域矣。故先儒曰。理一而分殊。正谓此也。不然则臣子何
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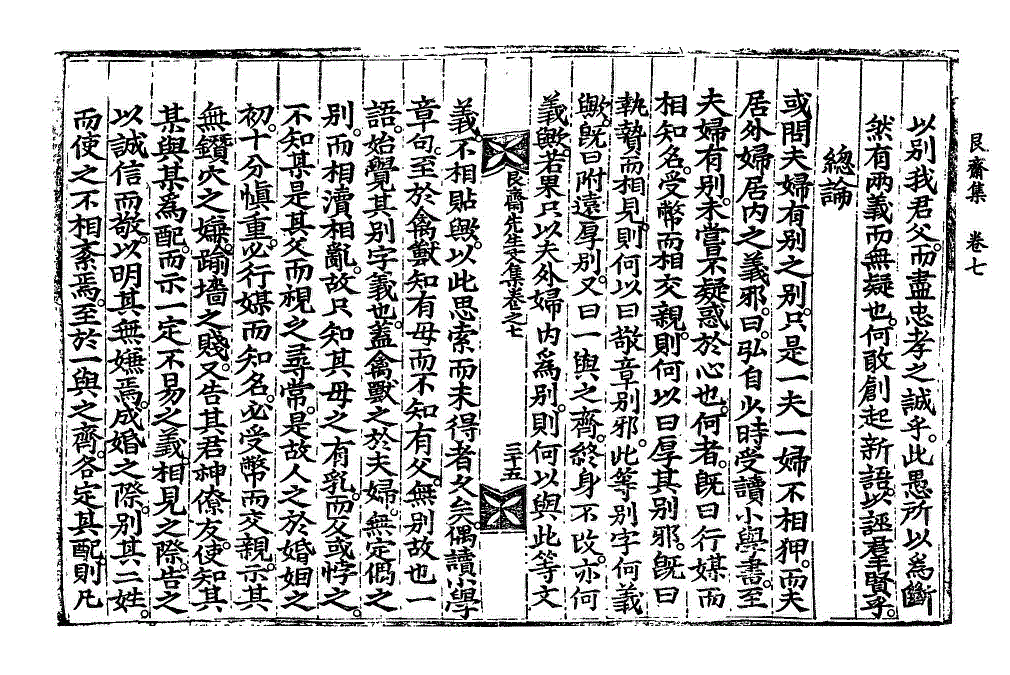 以别我君父。而尽忠孝之诚乎。此愚所以为断然有两义而无疑也。何敢创起新语。以诬群贤乎。
以别我君父。而尽忠孝之诚乎。此愚所以为断然有两义而无疑也。何敢创起新语。以诬群贤乎。总论
或问夫妇有别之别。只是一夫一妇不相狎。而夫居外妇居内之义邪。曰。弘自少时受读小学书。至夫妇有别。未尝不疑惑于心也。何者。既曰行媒而相知名。受币而相交亲。则何以曰厚其别邪。既曰执贽而相见。则何以曰敬章别邪。此等别字何义欤。既曰附远厚别。又曰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亦何义欤。若果只以夫外妇内为别。则何以与此等文义。不相贴欤。以此思索而未得者久矣。偶读小学章句。至于禽兽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无别故也一语。始觉其别字义也。盖禽兽之于夫妇。无定偶之别。而相渎相乱。故只知其母之有乳。而反或悖之。不知某是其父而视之寻常。是故人之于婚姻之初。十分慎重。必行媒而知名。必受币而交亲。示其无钻穴之嫌。踰墙之贱。又告其君神僚友。使知其某与某为配。而示一定不易之义。相见之际。告之以诚信而敬。以明其无嫌焉。成婚之际。别其二姓。而使之不相紊焉。至于一与之齐。各定其配。则凡
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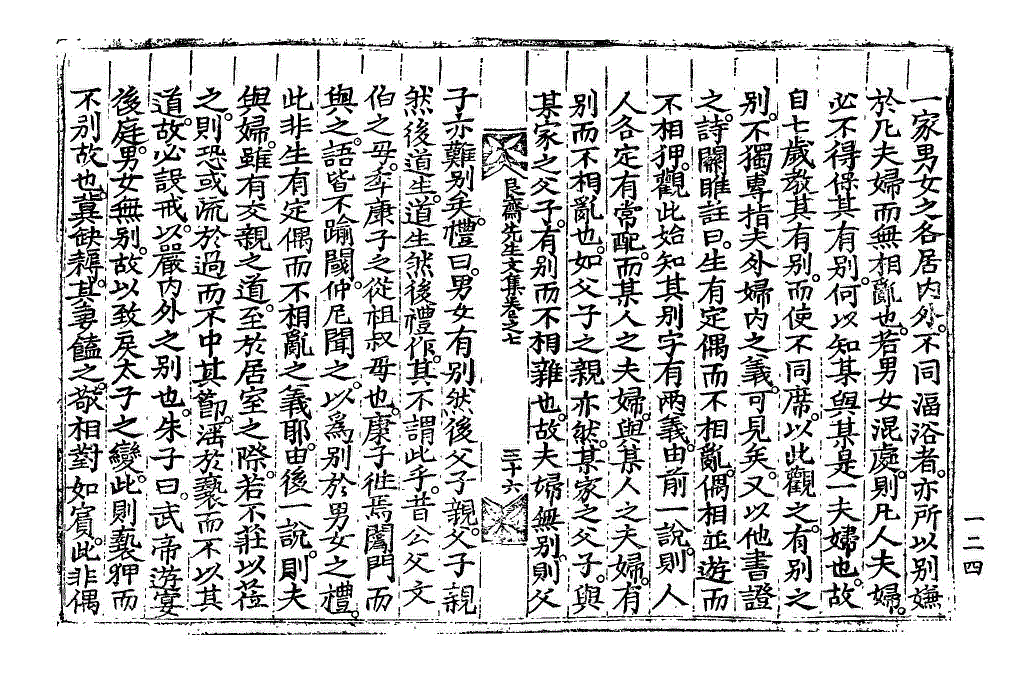 一家男女之各居内外。不同湢浴者。亦所以别嫌于凡夫妇而无相乱也。若男女混处。则凡人夫妇。必不得保其有别。何以知某与某是一夫妇也。故自七岁教其有别。而使不同席。以此观之。有别之别。不独专指夫外妇内之义。可见矣。又以他书證之。诗关雎注曰。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相并游而不相狎。观此始知其别字有两义。由前一说。则人人各定有常配。而某人之夫妇。与某人之夫妇。有别而不相乱也。如父子之亲亦然。某家之父子。与某家之父子。有别而不相杂也。故夫妇无别。则父子亦难别矣。礼曰。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道生。道生然后礼作。其不谓此乎。昔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从祖叔母也。康子往焉䦱门而与之。语皆不踰阈。仲尼闻之。以为别于男女之礼。此非生有定偶而不相乱之义耶。由后一说。则夫与妇。虽有交亲之道。至于居室之际。若不庄以莅之。则恐或流于过而不中其节。淫于亵而不以其道。故必设戒。以严内外之别也。朱子曰。武帝游宴后庭。男女无别。故以致戾太子之变。此则亵狎而不别故也。冀缺耨。其妻馌之。敬相对如宾。此非偶
一家男女之各居内外。不同湢浴者。亦所以别嫌于凡夫妇而无相乱也。若男女混处。则凡人夫妇。必不得保其有别。何以知某与某是一夫妇也。故自七岁教其有别。而使不同席。以此观之。有别之别。不独专指夫外妇内之义。可见矣。又以他书證之。诗关雎注曰。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相并游而不相狎。观此始知其别字有两义。由前一说。则人人各定有常配。而某人之夫妇。与某人之夫妇。有别而不相乱也。如父子之亲亦然。某家之父子。与某家之父子。有别而不相杂也。故夫妇无别。则父子亦难别矣。礼曰。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道生。道生然后礼作。其不谓此乎。昔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从祖叔母也。康子往焉䦱门而与之。语皆不踰阈。仲尼闻之。以为别于男女之礼。此非生有定偶而不相乱之义耶。由后一说。则夫与妇。虽有交亲之道。至于居室之际。若不庄以莅之。则恐或流于过而不中其节。淫于亵而不以其道。故必设戒。以严内外之别也。朱子曰。武帝游宴后庭。男女无别。故以致戾太子之变。此则亵狎而不别故也。冀缺耨。其妻馌之。敬相对如宾。此非偶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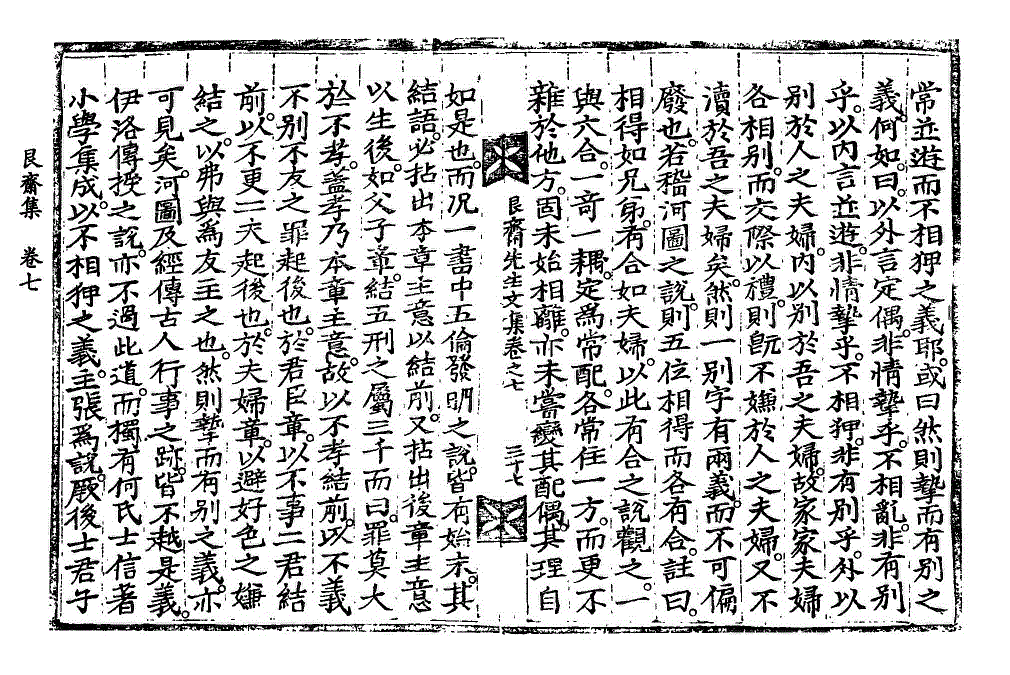 常并游而不相狎之义邪。或曰然则挚而有别之义。何如。曰。以外言定偶。非情挚乎。不相乱。非有别乎。以内言并游。非情挚乎。不相狎。非有别乎。外以别于人之夫妇。内以别于吾之夫妇。故家家夫妇各相别。而交际以礼。则既不嫌于人之夫妇。又不渎于吾之夫妇矣。然则一别字有两义。而不可偏废也。若稽河图之说。则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注曰。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妇。以此有合之说观之。一与六合。一奇一耦。定为常配。各常住一方。而更不杂于他方。固未始相离。亦未尝变其配偶。其理自如是也。而况一书中五伦发明之说。皆有始末。其结语。必拈出本章主意以结前。又拈出后章主意以生后。如父子章。结五刑之属三千而曰。罪莫大于不孝。盖孝乃本章主意。故以不孝结前。以不义不别不友之罪起后也。于君臣章。而不事二君结前。以不更二夫起后也。于夫妇章。以避好色之嫌结之。以弗与为友主之也。然则挚而有别之义。亦可见矣。河图及经传古人行事之迹。皆不越是义。伊洛传授之说。亦不过此道。而独有何氏士信著小学集成。以不相狎之义。主张为说。厥后士君子
常并游而不相狎之义邪。或曰然则挚而有别之义。何如。曰。以外言定偶。非情挚乎。不相乱。非有别乎。以内言并游。非情挚乎。不相狎。非有别乎。外以别于人之夫妇。内以别于吾之夫妇。故家家夫妇各相别。而交际以礼。则既不嫌于人之夫妇。又不渎于吾之夫妇矣。然则一别字有两义。而不可偏废也。若稽河图之说。则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注曰。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妇。以此有合之说观之。一与六合。一奇一耦。定为常配。各常住一方。而更不杂于他方。固未始相离。亦未尝变其配偶。其理自如是也。而况一书中五伦发明之说。皆有始末。其结语。必拈出本章主意以结前。又拈出后章主意以生后。如父子章。结五刑之属三千而曰。罪莫大于不孝。盖孝乃本章主意。故以不孝结前。以不义不别不友之罪起后也。于君臣章。而不事二君结前。以不更二夫起后也。于夫妇章。以避好色之嫌结之。以弗与为友主之也。然则挚而有别之义。亦可见矣。河图及经传古人行事之迹。皆不越是义。伊洛传授之说。亦不过此道。而独有何氏士信著小学集成。以不相狎之义。主张为说。厥后士君子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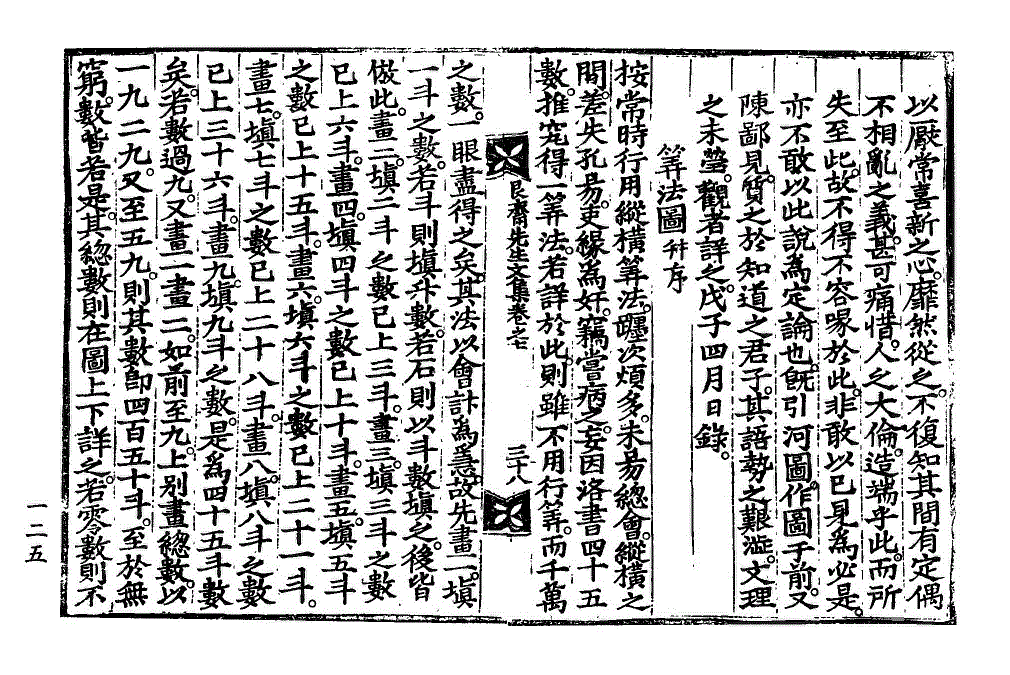 以厌常喜新之心。靡然从之。不复知其间有定偶不相乱之义。甚可痛惜。人之大伦。造端乎此。而所失至此。故不得不容喙于此。非敢以己见为必是。亦不敢以此说为定论也。既引河图。作图于前。又陈鄙见。质之于知道之君子。其语势之艰涩。文理之未莹。观者详之。戊子四月日录。
以厌常喜新之心。靡然从之。不复知其间有定偶不相乱之义。甚可痛惜。人之大伦。造端乎此。而所失至此。故不得不容喙于此。非敢以己见为必是。亦不敢以此说为定论也。既引河图。作图于前。又陈鄙见。质之于知道之君子。其语势之艰涩。文理之未莹。观者详之。戊子四月日录。算法图(并序)
按常时行用纵横算法。躔次烦多。未易总会。纵横之间。差失孔易。吏缘为奸。窃尝病之。妄因洛书四十五数。推究得一算法。若详于此。则虽不用行算。而千万之数。一眼尽得之矣。其法以会计为急。故先画一。填一斗之数。若斗则填升数。若石则以斗数填之。后皆仿此。画二。填二斗之数已上三斗。画三。填三斗之数已上六斗。画四。填四斗之数已上十斗。画五。填五斗之数已上十五斗。画六。填六斗之数已上二十一斗。画七。填七斗之数已上二十八斗。画八。填八斗之数已上三十六斗。画九。填九斗之数。是为四十五斗数矣。若数过九。又画一画二。如前至九。上别画总数。以一九二九。又至五九。则其数即四百五十斗。至于无穷。数皆若是。其总数则在图上下详之。若零数则不
艮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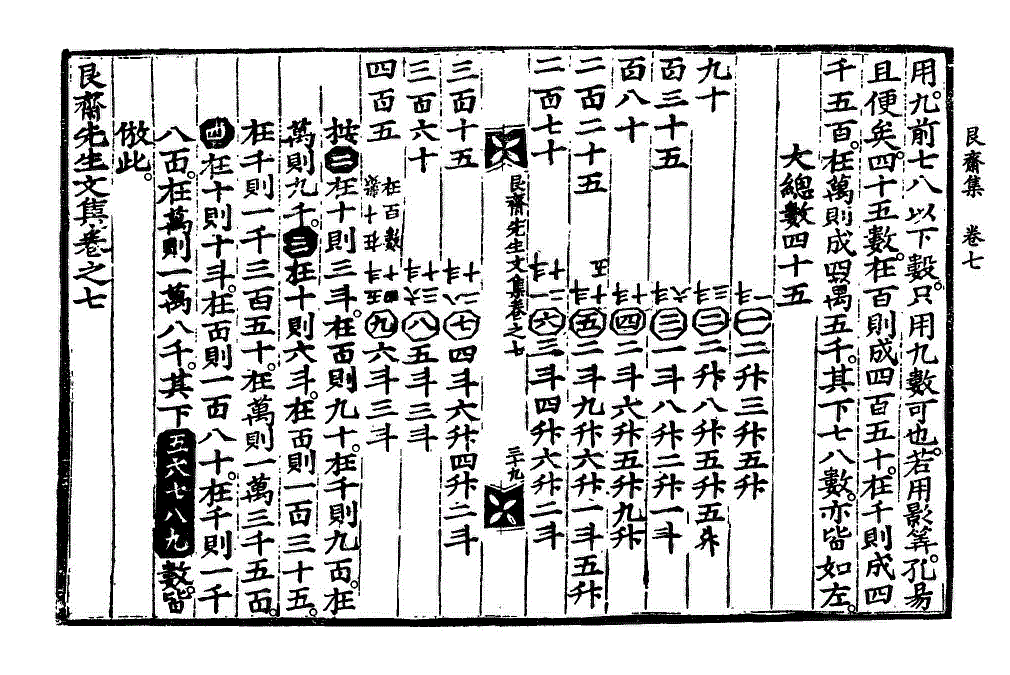 用九。前七八以下数。只用九数可也。若用影算。孔易且便矣。四十五数。在百则成四百五十。在千则成四千五百。在万则成四万五千。其下七八数。亦皆如左。
用九。前七八以下数。只用九数可也。若用影算。孔易且便矣。四十五数。在百则成四百五十。在千则成四千五百。在万则成四万五千。其下七八数。亦皆如左。大总数四十五
一斗㊀二升三升五升
九十三斗㊁二升八升五升五升
百三十五六斗㊂一斗八升二升一斗
百八十十斗㊃二斗六升五升九升
二百二十五十五斗㊄二斗九升六升一斗五升
二百七十二十一斗㊅三斗四升六升二斗
三百十五二十八斗㊆四斗六升四升二斗
三百六十三十六斗㊇五斗三斗
四百五在百数四十五斗㊈六斗三斗
在十数
按二在十则三斗。在百则九十。在千则九百。在万则九千。三在十则六斗。在百则一百三十五。在千则一千三百五十。在万则一万三千五百。四在十则十斗。在百则一百八十。在千则一千八百。在万则一万八千。其下五六七八九数。皆仿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