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x 页
松江别集卷之七
附录
附录
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3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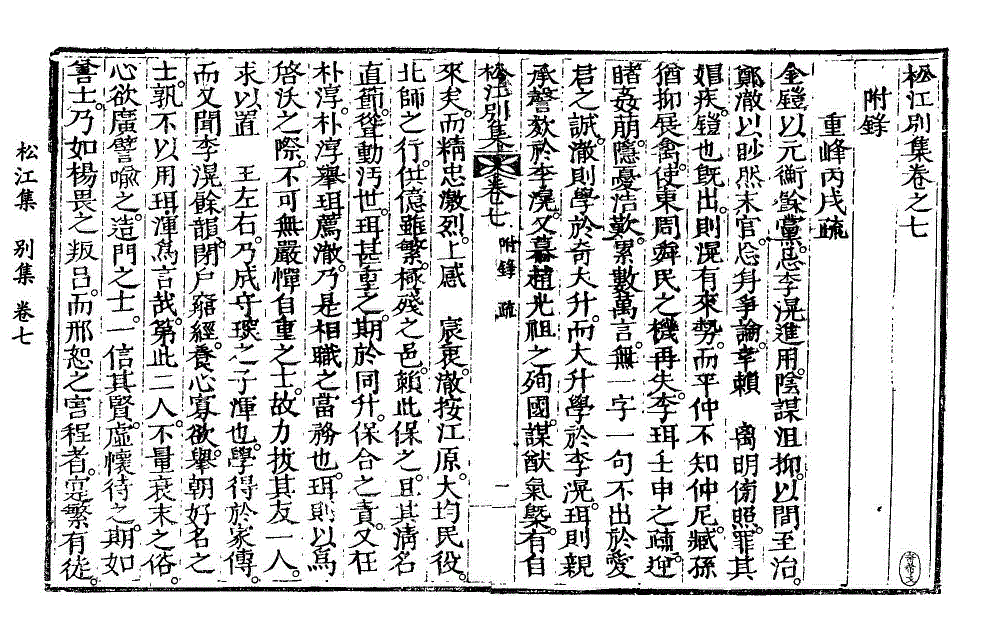 重峰丙戌疏
重峰丙戌疏金铠以元衡馀党。忌李滉进用。阴谋沮抑。以间至治。郑澈以眇然末官。忘身争论。幸赖 离明傍照。罪其媢疾。铠也既出。则滉有来势。而平仲不知仲尼。臧孙犹抑展禽。使东周舜民之机再失。李珥壬申之疏。逆睹奸萌。隐忧浩叹。累数万言。无一字一句不出于爱君之诚。澈则学于奇大升。而大升学于李滉。珥则亲承謦欬于李滉。又幕赵光祖之殉国。谋猷气概。有自来矣。而精忠激烈。上感 宸衷。澈按江原。大均民役。北师之行。供亿虽繁。极残之邑。赖此保之。且其清名直节。耸动污世。珥甚重之。期于同升。保合之责。又在朴淳。朴淳举珥荐澈。乃是相职之当务也。珥则以为启沃之际。不可无严惮自重之士。故力拔其友一人。求以置 王左右。乃成守琛之子浑也。学得于家传。而又闻李滉馀韵。闭户穷经。养心寡欲。举朝好名之士。孰不以用珥,浑为言哉。第此二人。不量衰末之俗。心欲广譬喻之。造门之士。一信其贤。虚怀待之。期如善士。乃如杨畏之叛吕。而邢恕之害程者。寔繁有徒。
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3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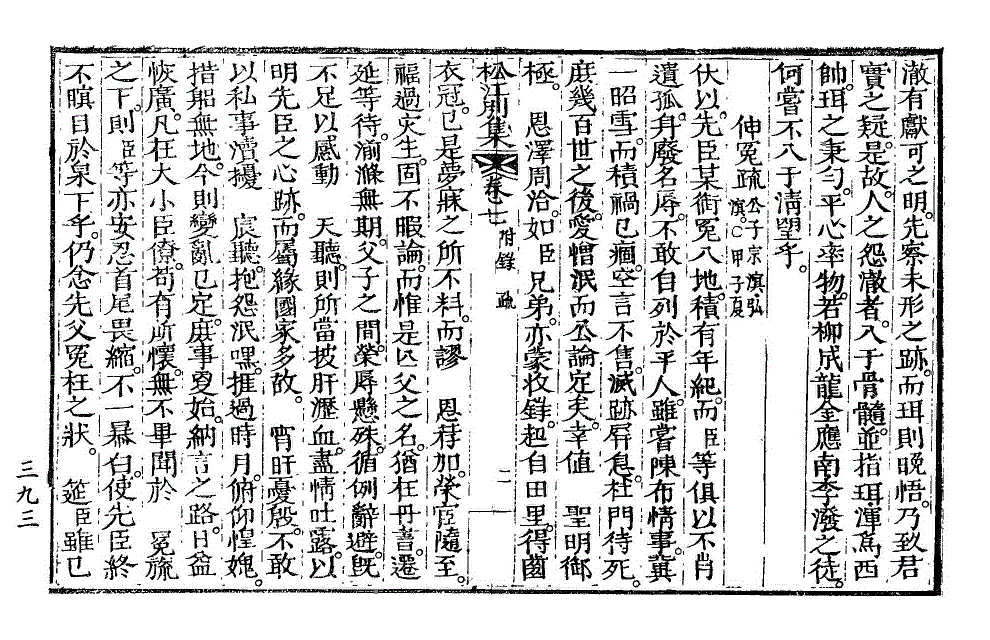 澈有献可之明。先察未形之迹。而珥则晚悟。乃致君实之疑。是故。人之怨澈者。入于骨髓。并指珥,浑为西帅。珥之秉匀。平心率物。若柳成龙,金应南,李泼之徒。何尝不入于清望乎。
澈有献可之明。先察未形之迹。而珥则晚悟。乃致君实之疑。是故。人之怨澈者。入于骨髓。并指珥,浑为西帅。珥之秉匀。平心率物。若柳成龙,金应南,李泼之徒。何尝不入于清望乎。伸冤疏(公子宗溟,弘溟。○甲子夏)
伏以。先臣某衔冤入地。积有年纪。而臣等俱以不肖遗孤。身废名辱。不敢自列于平人。虽尝陈布情事。冀一昭雪。而积祸已痼。空言不售。灭迹屏息。杜门待死。庶几百世之后。爱憎泯而公论定矣。幸值 圣明御极。 恩泽周洽。如臣兄弟。亦蒙收录。起自田里。得齿衣冠。已是梦寐之所不料。而谬 恩荐加。荣宦随至。福过灾生。固不暇论。而惟是亡父之名。犹在丹书。迁延等待。湔涤无期。父子之间。荣辱悬殊。循例辞避。既不足以感动 天听。则所当披肝沥血。尽情吐露。以明先臣之心迹。而属缘国家多故。 宵旰忧殷。不敢以私事渎扰 宸听。抱怨泯默。挨过时月。俯仰惶愧。措躬无地。今则变乱已定。庶事更始。纳言之路。日益恢广。凡在大小臣僚。苟有所怀。无不毕闻于 冕旒之下。则臣等亦安忍首尾畏缩。不一暴白。使先臣终不瞑目于泉下乎。仍念先父冤枉之状。 筵臣虽已
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394H 页
 陈达。 圣明虽已洞烛。而其间曲折。有非一时一言之所可备悉。玆敢不避烦冒。罗列如左。伏愿 圣明财察焉。臣父之所以被罪者。无他。不过以己丑治狱一事为言耳。当时论者。初以搆杀崔永庆为罪。其后日生新语。展转增益。至以李泼,李洁,白惟让之死。亦以为皆由于臣父之挟憾搆陷。其他连累而死者。悉以归怨于臣父。以其事在既往。辨證无据。牵合传会。无所不至。臣等不得不据实陈辨。当时逆贼。出于从班。二百年来。未有此变。臣父是时。以前赞成退在畿甸。闻变震惊。奔问 阙下。 圣教丁宁。许以忠节。未几。擢居台铉。仍 命以委官治狱。得见逆家文书。多举臣父之名。臣父即以形迹嫌疑。辞避乞免。而未蒙 允许。黾勉视事。以此弥增惶恐。凡干鞫问。动皆裁禀 圣旨。未尝径自擅断。时或越例献谳。多所伸理。岂敢有所轻重于其间。如言者所云云乎。当初逆徒有李光秀者纳招曰。郑八龙,吉三峰为大将云云。又有朴杙,朴延龄等招曰。非吉三峰。乃崔三峰也。三峰居在智异山下。与逆贼开山径往来。三峰常坐汝立之上。及问三峰容体则曰。面瘦黑。髯长至腹云云。于是。蜚语喧腾。莫适所指。一日。 先王下教三省曰。所
陈达。 圣明虽已洞烛。而其间曲折。有非一时一言之所可备悉。玆敢不避烦冒。罗列如左。伏愿 圣明财察焉。臣父之所以被罪者。无他。不过以己丑治狱一事为言耳。当时论者。初以搆杀崔永庆为罪。其后日生新语。展转增益。至以李泼,李洁,白惟让之死。亦以为皆由于臣父之挟憾搆陷。其他连累而死者。悉以归怨于臣父。以其事在既往。辨證无据。牵合传会。无所不至。臣等不得不据实陈辨。当时逆贼。出于从班。二百年来。未有此变。臣父是时。以前赞成退在畿甸。闻变震惊。奔问 阙下。 圣教丁宁。许以忠节。未几。擢居台铉。仍 命以委官治狱。得见逆家文书。多举臣父之名。臣父即以形迹嫌疑。辞避乞免。而未蒙 允许。黾勉视事。以此弥增惶恐。凡干鞫问。动皆裁禀 圣旨。未尝径自擅断。时或越例献谳。多所伸理。岂敢有所轻重于其间。如言者所云云乎。当初逆徒有李光秀者纳招曰。郑八龙,吉三峰为大将云云。又有朴杙,朴延龄等招曰。非吉三峰。乃崔三峰也。三峰居在智异山下。与逆贼开山径往来。三峰常坐汝立之上。及问三峰容体则曰。面瘦黑。髯长至腹云云。于是。蜚语喧腾。莫适所指。一日。 先王下教三省曰。所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3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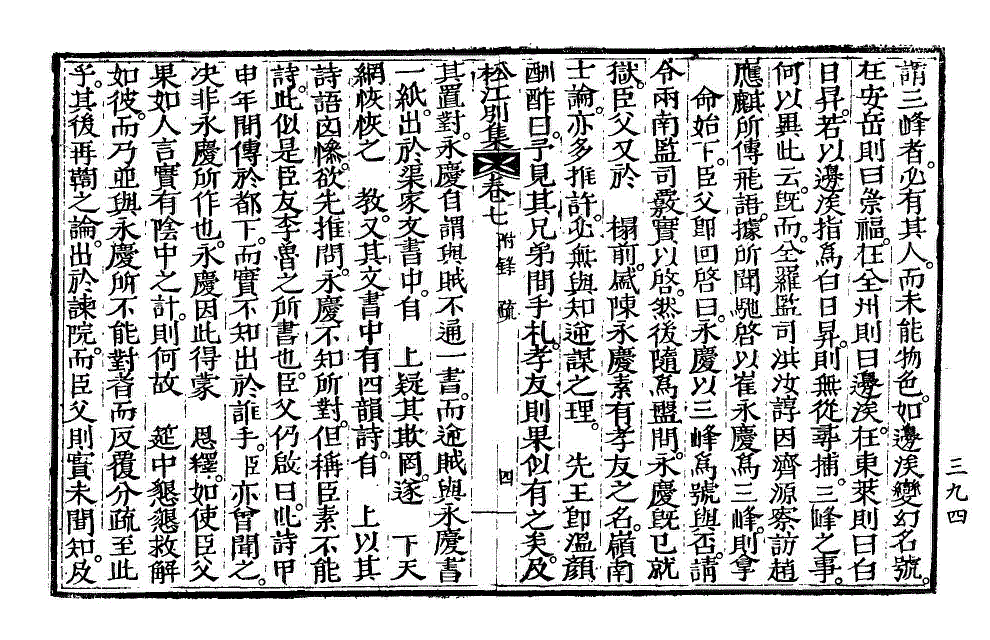 谓三峰者。必有其人。而未能物色。如边涘变幻名号。在安岳则曰崇福。在全州则曰边涘。在东莱则曰白日升。若以边涘指为白日升。则无从寻捕。三峰之事。何以异此云。既而。全罗监司洪汝谆因济源察访赵应麒所传飞语。据所闻驰启以崔永庆为三峰。则拿 命始下。臣父即回启曰。永庆以三峰为号与否。请令两南监司覈实以启。然后随为盘问。永庆既已就狱。臣父又于 榻前。盛陈永庆素有孝友之名。岭南士论。亦多推许。必无与知逆谋之理。 先王即温颜酬酢曰。予见其兄弟间手札。孝友则果似有之矣。及其置对。永庆自谓与贼不通一书。而逆贼与永庆书一纸。出于渠家文书中。自 上疑其欺罔。遂 下天网恢恢之 教。又其文书中有四韵诗。自 上以其诗语凶惨。欲先推问。永庆不知所对。但称臣素不能诗。此似是臣友李鲁之所书也。臣父仍启曰。此诗甲申年间传于都下。而实不知出于谁手。臣亦曾闻之。决非永庆所作也。永庆因此得蒙 恩释。如使臣父果如人言实有阴中之计。则何故 筵中恳恳救解如彼。而乃并与永庆所不能对者而反覆分疏至此乎。其后再鞫之论。出于谏院。而臣父则实未闻知。及
谓三峰者。必有其人。而未能物色。如边涘变幻名号。在安岳则曰崇福。在全州则曰边涘。在东莱则曰白日升。若以边涘指为白日升。则无从寻捕。三峰之事。何以异此云。既而。全罗监司洪汝谆因济源察访赵应麒所传飞语。据所闻驰启以崔永庆为三峰。则拿 命始下。臣父即回启曰。永庆以三峰为号与否。请令两南监司覈实以启。然后随为盘问。永庆既已就狱。臣父又于 榻前。盛陈永庆素有孝友之名。岭南士论。亦多推许。必无与知逆谋之理。 先王即温颜酬酢曰。予见其兄弟间手札。孝友则果似有之矣。及其置对。永庆自谓与贼不通一书。而逆贼与永庆书一纸。出于渠家文书中。自 上疑其欺罔。遂 下天网恢恢之 教。又其文书中有四韵诗。自 上以其诗语凶惨。欲先推问。永庆不知所对。但称臣素不能诗。此似是臣友李鲁之所书也。臣父仍启曰。此诗甲申年间传于都下。而实不知出于谁手。臣亦曾闻之。决非永庆所作也。永庆因此得蒙 恩释。如使臣父果如人言实有阴中之计。则何故 筵中恳恳救解如彼。而乃并与永庆所不能对者而反覆分疏至此乎。其后再鞫之论。出于谏院。而臣父则实未闻知。及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3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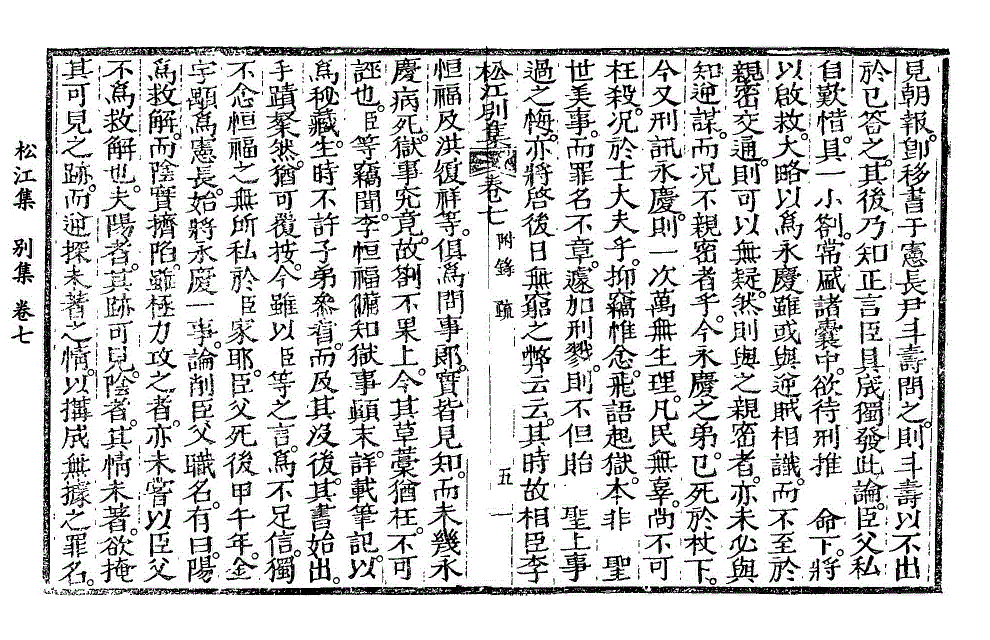 见朝报。即移书于宪长尹斗寿问之。则斗寿以不出于已答之。其后乃知正言臣具宬独发此论。臣父私自叹惜。具一小劄。常盛诸囊中。欲待刑推 命下。将以启救。大略以为永庆虽或与逆贼相识。而不至于亲密交通。则可以无疑。然则与之亲密者。亦未必与知逆谋。而况不亲密者乎。今永庆之弟。已死于杖下。今又刑讯永庆。则一次万无生理。凡民无辜。尚不可枉杀。况于士大夫乎。抑窃惟念。飞语起狱。本非 圣世美事。而罪名不章。遽加刑戮。则不但贻 圣上事过之悔。亦将启后日无穷之弊云云。其时故相臣李恒福及洪履祥等。俱为问事郎。实皆见知。而未几永庆病死。狱事究竟。故劄不果上。今其草藁犹在。不可诬也。臣等窃闻。李恒福备知狱事颠末。详载笔记。以为秘藏。生时不许子弟参看。而及其没后。其书始出。手迹粲然。犹可覆按。今虽以臣等之言。为不足信。独不念恒福之无所私于臣家耶。臣父死后甲午年。金宇颙为宪长。始将永庆一事。论削臣父职名。有曰。阳为救解。而阴实挤陷。虽极力攻之者。亦未尝以臣父不为救解也。夫阳者。其迹可见。阴者。其情未著。欲掩其可见之迹。而逆探未著之情。以搆成无据之罪名。
见朝报。即移书于宪长尹斗寿问之。则斗寿以不出于已答之。其后乃知正言臣具宬独发此论。臣父私自叹惜。具一小劄。常盛诸囊中。欲待刑推 命下。将以启救。大略以为永庆虽或与逆贼相识。而不至于亲密交通。则可以无疑。然则与之亲密者。亦未必与知逆谋。而况不亲密者乎。今永庆之弟。已死于杖下。今又刑讯永庆。则一次万无生理。凡民无辜。尚不可枉杀。况于士大夫乎。抑窃惟念。飞语起狱。本非 圣世美事。而罪名不章。遽加刑戮。则不但贻 圣上事过之悔。亦将启后日无穷之弊云云。其时故相臣李恒福及洪履祥等。俱为问事郎。实皆见知。而未几永庆病死。狱事究竟。故劄不果上。今其草藁犹在。不可诬也。臣等窃闻。李恒福备知狱事颠末。详载笔记。以为秘藏。生时不许子弟参看。而及其没后。其书始出。手迹粲然。犹可覆按。今虽以臣等之言。为不足信。独不念恒福之无所私于臣家耶。臣父死后甲午年。金宇颙为宪长。始将永庆一事。论削臣父职名。有曰。阳为救解。而阴实挤陷。虽极力攻之者。亦未尝以臣父不为救解也。夫阳者。其迹可见。阴者。其情未著。欲掩其可见之迹。而逆探未著之情。以搆成无据之罪名。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3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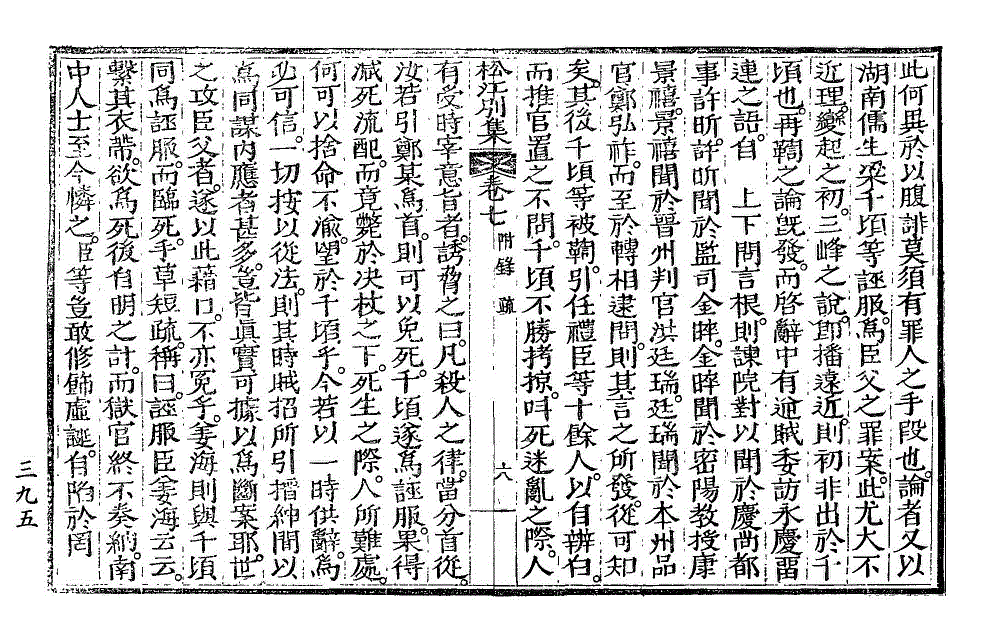 此何异于以腹诽,莫须有罪人之手段也。论者又以湖南儒生梁千顷等诬服。为臣父之罪案。此尤大不近理。变起之初。三峰之说。即播远近。则初非出于千顷也。再鞫之论既发。而启辞中有逆贼委访永庆留连之语。自 上下问言根。则谏院对以闻于庆尚都事许昕。许昕闻于监司金晬。金晬闻于密阳教授康景禧。景禧闻于晋州判官洪廷瑞。廷瑞闻于本州品官郑弘祚。而至于转相逮问。则其言之所发。从可知矣。其后千顷等被鞫。引任礼臣等十馀人。以自辨白。而推官置之不问。千顷不胜拷掠。叫死迷乱之际。人有受时宰意旨者。诱胁之曰。凡杀人之律。当分首从。汝若引郑某为首。则可以免死。千顷遂为诬服。果得减死流配。而竟毙于决杖之下。死生之际。人所难处。何可以舍命不渝。望于千顷乎。今若以一时供辞。为必可信。一切按以从法。则其时贼招所引搢绅闻以为同谋内应者甚多。岂皆真实可据以为断案耶。世之攻臣父者。遂以此藉口。不亦冤乎。姜海则与千顷同为诬服。而临死。手草短疏。称曰。诬服臣姜海云云。系其衣带。欲为死后自明之计。而狱官终不奏纳。南中人士至今怜之。臣等岂敢修饰虚诞。自陷于罔
此何异于以腹诽,莫须有罪人之手段也。论者又以湖南儒生梁千顷等诬服。为臣父之罪案。此尤大不近理。变起之初。三峰之说。即播远近。则初非出于千顷也。再鞫之论既发。而启辞中有逆贼委访永庆留连之语。自 上下问言根。则谏院对以闻于庆尚都事许昕。许昕闻于监司金晬。金晬闻于密阳教授康景禧。景禧闻于晋州判官洪廷瑞。廷瑞闻于本州品官郑弘祚。而至于转相逮问。则其言之所发。从可知矣。其后千顷等被鞫。引任礼臣等十馀人。以自辨白。而推官置之不问。千顷不胜拷掠。叫死迷乱之际。人有受时宰意旨者。诱胁之曰。凡杀人之律。当分首从。汝若引郑某为首。则可以免死。千顷遂为诬服。果得减死流配。而竟毙于决杖之下。死生之际。人所难处。何可以舍命不渝。望于千顷乎。今若以一时供辞。为必可信。一切按以从法。则其时贼招所引搢绅闻以为同谋内应者甚多。岂皆真实可据以为断案耶。世之攻臣父者。遂以此藉口。不亦冤乎。姜海则与千顷同为诬服。而临死。手草短疏。称曰。诬服臣姜海云云。系其衣带。欲为死后自明之计。而狱官终不奏纳。南中人士至今怜之。臣等岂敢修饰虚诞。自陷于罔 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3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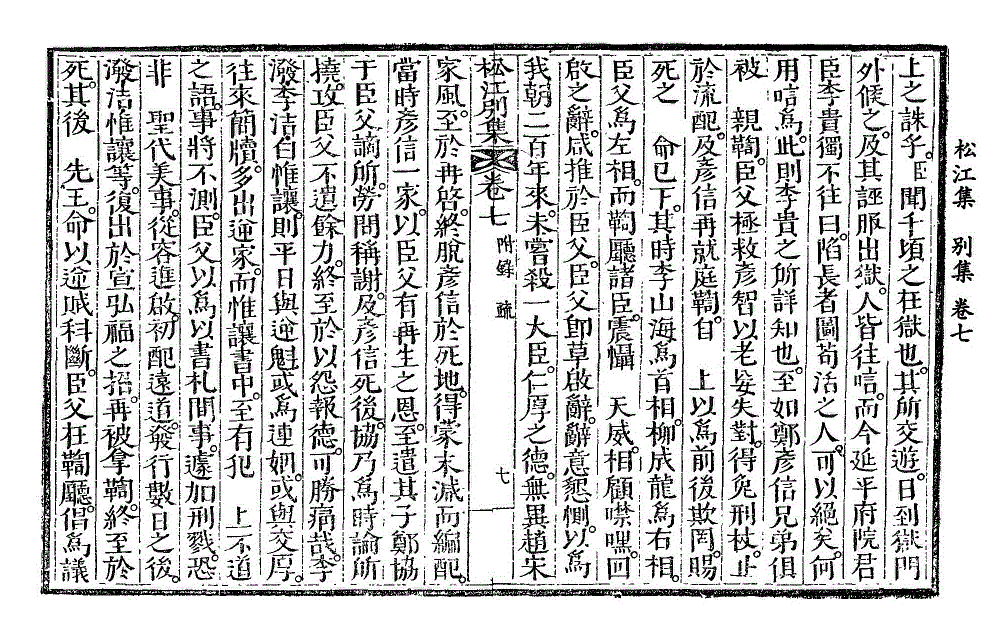 上之诛乎。臣闻千顷之在狱也。其所交游。日到狱门外候之。及其诬服出狱。人皆往唁。而今延平府院君臣李贵独不往曰。陷长者图苟活之人。可以绝矣。何用唁为。此则李贵之所详知也。至如郑彦信兄弟俱被 亲鞫。臣父极救彦智以老妄失对。得免刑杖。止于流配。及彦信再就庭鞫。自 上以为前后欺罔。赐死之 命已下。其时李山海为首相。柳成龙为右相。臣父为左祖。而鞫听诸臣。震慑 天威。相顾噤默。回启之辞。咸推于臣父。臣父即草启辞。辞意恳恻。以为我朝二百年来。未尝杀一大臣。仁厚之德。无异赵宋家风。至于再启。终脱彦信于死地。得蒙末减而编配。当时彦信一家。以臣父有再生之恩。至遣其子郑协于臣父谪所。劳问称谢。及彦信死后。协乃为时论所挠。攻臣父不遗馀力。终至于以怨报德。可胜痛哉。李泼,李洁,白惟让。则平日与逆魁或为连姻。或与交厚。往来简牍。多出逆家。而惟让书中。至有犯 上不道之语。事将不测。臣父以为以书札间事。遽加刑戮。恐非 圣代美事。从容进启。初配远道。发行数日之后。泼,洁,惟让等。复出于宣弘福之招。再被拿鞫。终至于死。其后 先王。命以逆贼科断。臣父在鞫厅。倡为议
上之诛乎。臣闻千顷之在狱也。其所交游。日到狱门外候之。及其诬服出狱。人皆往唁。而今延平府院君臣李贵独不往曰。陷长者图苟活之人。可以绝矣。何用唁为。此则李贵之所详知也。至如郑彦信兄弟俱被 亲鞫。臣父极救彦智以老妄失对。得免刑杖。止于流配。及彦信再就庭鞫。自 上以为前后欺罔。赐死之 命已下。其时李山海为首相。柳成龙为右相。臣父为左祖。而鞫听诸臣。震慑 天威。相顾噤默。回启之辞。咸推于臣父。臣父即草启辞。辞意恳恻。以为我朝二百年来。未尝杀一大臣。仁厚之德。无异赵宋家风。至于再启。终脱彦信于死地。得蒙末减而编配。当时彦信一家。以臣父有再生之恩。至遣其子郑协于臣父谪所。劳问称谢。及彦信死后。协乃为时论所挠。攻臣父不遗馀力。终至于以怨报德。可胜痛哉。李泼,李洁,白惟让。则平日与逆魁或为连姻。或与交厚。往来简牍。多出逆家。而惟让书中。至有犯 上不道之语。事将不测。臣父以为以书札间事。遽加刑戮。恐非 圣代美事。从容进启。初配远道。发行数日之后。泼,洁,惟让等。复出于宣弘福之招。再被拿鞫。终至于死。其后 先王。命以逆贼科断。臣父在鞫厅。倡为议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3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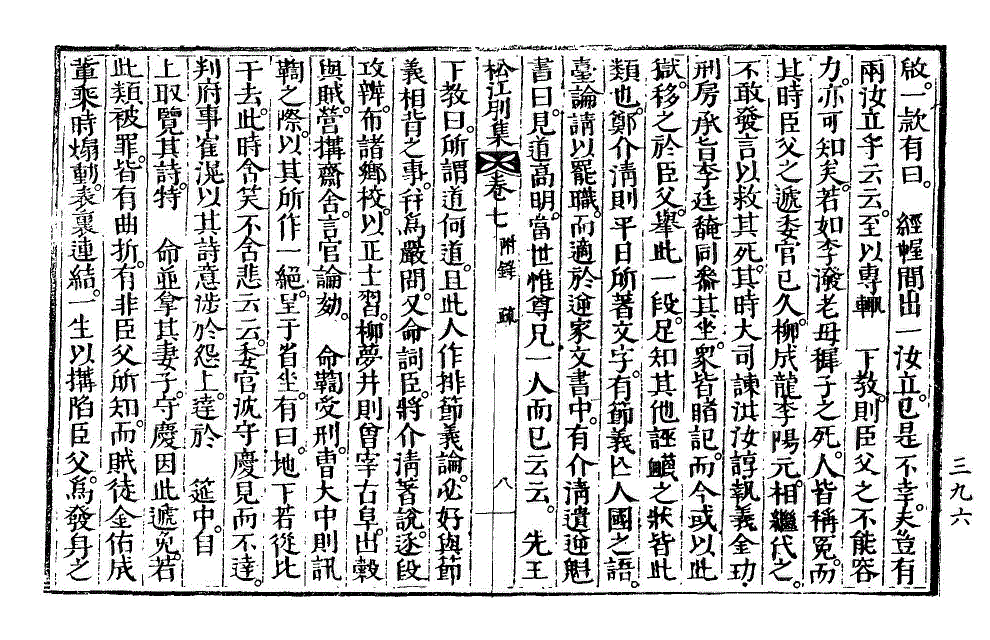 启。一款有曰。 经幄间出一汝立。已是不幸。夫岂有两汝立乎云云。至以专辄 下教。则臣父之不能容力。亦可知矣。若如李泼老母稚子之死。人皆称冤。而其时臣父之递委官已久。柳成龙,李阳元。相继代之。不敢发言以救其死。其时大司谏洪汝谆,执义金玏,刑房承旨李廷馣同参其坐。众皆睹记。而今或以此狱。移之于臣父。举此一段。足知其他诬蔑之状皆此类也。郑介清则平日所著文字。有节义亡人国之语。台论请以罢职。而适于逆家文书中。有介清遗逆魁书曰。见道高明。当世惟尊兄一人而已云云。 先王下教曰。所谓道何道。且此人作排节义论。必好与节义相背之事。并为严问。又命词臣。将介清著说。逐段攻辨。布诸乡校。以正士习。柳梦井则曾宰古阜。出谷与贼。营搆斋舍。言官论劾。 命鞫受刑。曹大中则讯鞫之际。以其所作一绝。呈于省坐。有曰。地下若从比干去。此时含笑不含悲云云。委官沈守庆见而不达。判府事崔滉以其诗意涉于怨上。达于 筵中。自 上取览其诗。特 命并拿其妻子。守庆因此递免。若此类被罪。皆有曲折。有非臣父所知。而贼徒金佑成辈乘时煽动。表里连结。一生以搆陷臣父。为发身之
启。一款有曰。 经幄间出一汝立。已是不幸。夫岂有两汝立乎云云。至以专辄 下教。则臣父之不能容力。亦可知矣。若如李泼老母稚子之死。人皆称冤。而其时臣父之递委官已久。柳成龙,李阳元。相继代之。不敢发言以救其死。其时大司谏洪汝谆,执义金玏,刑房承旨李廷馣同参其坐。众皆睹记。而今或以此狱。移之于臣父。举此一段。足知其他诬蔑之状皆此类也。郑介清则平日所著文字。有节义亡人国之语。台论请以罢职。而适于逆家文书中。有介清遗逆魁书曰。见道高明。当世惟尊兄一人而已云云。 先王下教曰。所谓道何道。且此人作排节义论。必好与节义相背之事。并为严问。又命词臣。将介清著说。逐段攻辨。布诸乡校。以正士习。柳梦井则曾宰古阜。出谷与贼。营搆斋舍。言官论劾。 命鞫受刑。曹大中则讯鞫之际。以其所作一绝。呈于省坐。有曰。地下若从比干去。此时含笑不含悲云云。委官沈守庆见而不达。判府事崔滉以其诗意涉于怨上。达于 筵中。自 上取览其诗。特 命并拿其妻子。守庆因此递免。若此类被罪。皆有曲折。有非臣父所知。而贼徒金佑成辈乘时煽动。表里连结。一生以搆陷臣父。为发身之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3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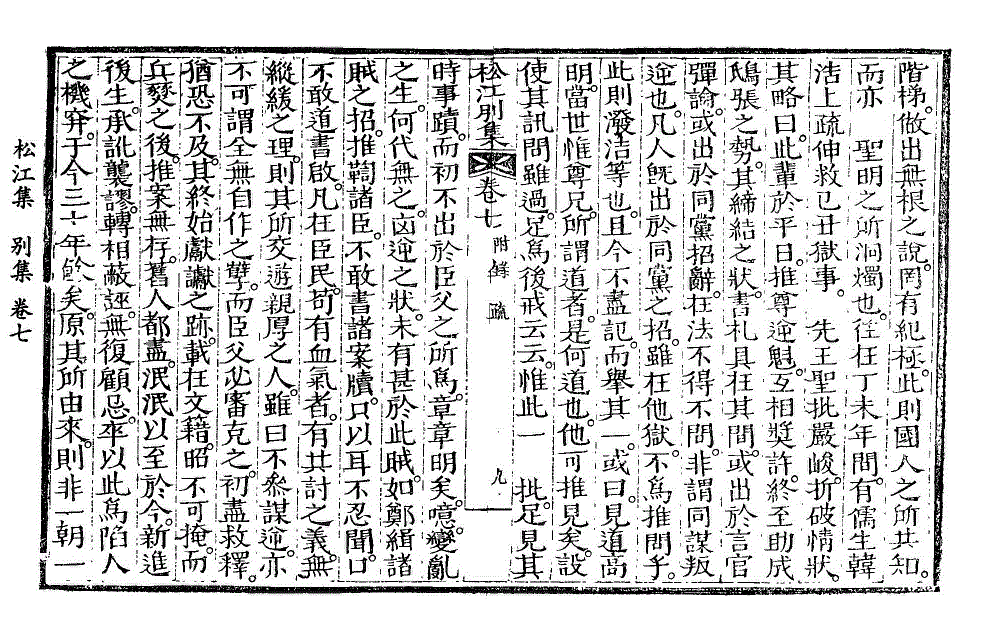 阶梯。做出无根之说。罔有纪极。此则国人之所共知。而亦 圣明之所洞烛也。往在丁未年间。有儒生韩浩上疏伸救己丑狱事。 先王圣批严峻。折破情状。其略曰。此辈于平日。推尊逆魁。互相奖许。终至助成鸱张之势。其缔结之状。书札具在其间。或出于言官弹论。或出于同党招辞。在法不得不问。非谓同谋叛逆也。凡人既出于同党之招。虽在他狱。不为推问乎。此则泼,洁等也。且今不尽记。而举其一。或曰。见道高明。当世惟尊兄。所谓道者。是何道也。他可推见矣。设使其讯问虽过。足为后戒云云。惟此一 批。足见其时事迹。而初不出于臣父之所为。章章明矣。噫。变乱之生。何代无之。凶逆之状。未有甚于此贼。如郑缉诸贼之招。推鞫诸臣。不敢书诸案牍。只以耳不忍闻。口不敢道书启。凡在臣民。苟有血气者。有共讨之义。无纵缓之理。则其所交游亲厚之人。虽曰不参谋逆。亦不可谓全无自作之孽。而臣父必审克之。初尽救释。犹恐不及。其终始献谳之迹。载在文籍。昭不可掩。而兵燹之后。推案无存。旧人都尽。泯泯以至于今。新进后生。承讹袭谬。转相蔽诬。无复顾忌。卒以此为陷人之机阱。于今三十年馀矣。原其所由来。则非一朝一
阶梯。做出无根之说。罔有纪极。此则国人之所共知。而亦 圣明之所洞烛也。往在丁未年间。有儒生韩浩上疏伸救己丑狱事。 先王圣批严峻。折破情状。其略曰。此辈于平日。推尊逆魁。互相奖许。终至助成鸱张之势。其缔结之状。书札具在其间。或出于言官弹论。或出于同党招辞。在法不得不问。非谓同谋叛逆也。凡人既出于同党之招。虽在他狱。不为推问乎。此则泼,洁等也。且今不尽记。而举其一。或曰。见道高明。当世惟尊兄。所谓道者。是何道也。他可推见矣。设使其讯问虽过。足为后戒云云。惟此一 批。足见其时事迹。而初不出于臣父之所为。章章明矣。噫。变乱之生。何代无之。凶逆之状。未有甚于此贼。如郑缉诸贼之招。推鞫诸臣。不敢书诸案牍。只以耳不忍闻。口不敢道书启。凡在臣民。苟有血气者。有共讨之义。无纵缓之理。则其所交游亲厚之人。虽曰不参谋逆。亦不可谓全无自作之孽。而臣父必审克之。初尽救释。犹恐不及。其终始献谳之迹。载在文籍。昭不可掩。而兵燹之后。推案无存。旧人都尽。泯泯以至于今。新进后生。承讹袭谬。转相蔽诬。无复顾忌。卒以此为陷人之机阱。于今三十年馀矣。原其所由来。则非一朝一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3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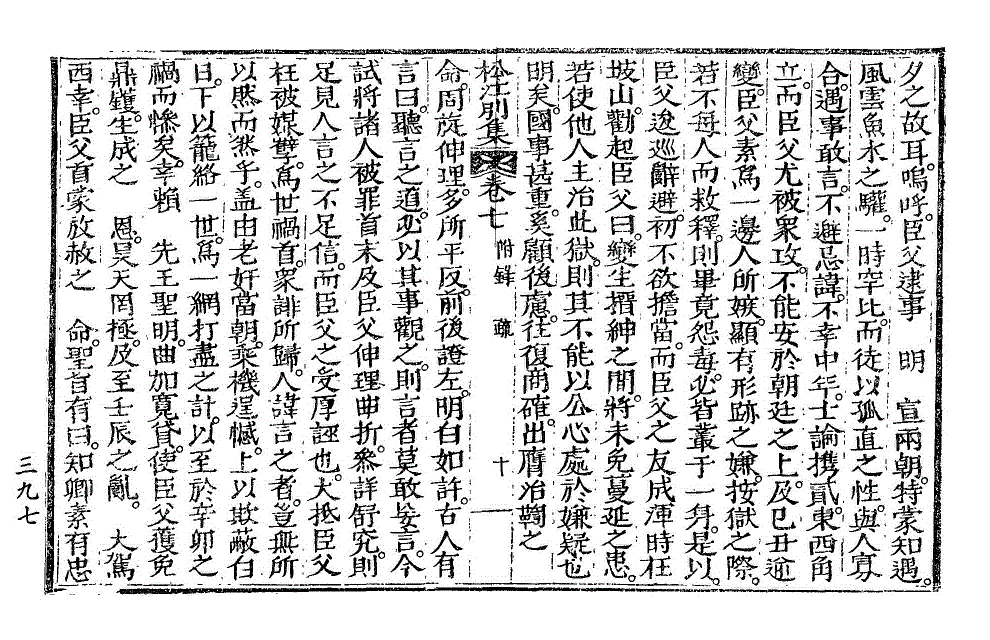 夕之故耳。呜呼。臣父逮事 明 宣两朝。特蒙知遇。风云鱼水之驩。一时罕比。而徒以孤直之性。与人寡合。遇事敢言。不避忌讳。不幸中年。士论携贰。东西角立。而臣父尤被众攻。不能安于朝廷之上。及己丑逾变。臣父素为一边人所嫉。显有形迹之嫌。按狱之际。若不每人而救释。则毕竟怨毒。必皆丛于一身。是以。臣父逡巡辞避。初不欲担当。而臣父之友成浑时在坡山。劝起臣父曰。变生搢绅之间。将未免蔓延之患。若使他人主治此狱。则其不能以公心处于嫌疑也明矣。国事甚重。奚顾后虑。往复商确。出膺治鞫之 命。周旋伸理。多所平反。前后證左。明白如许。古人有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试将诸人被罪首末及臣父伸理曲折。参详舒究。则足见人言之不足信。而臣父之受厚诬也。大抵臣父枉被媒孽。为世祸首。众诽所归。人讳言之者。岂无所以然而然乎。盖由老奸当朝。乘机逞憾。上以欺蔽白日。下以笼络一世。为一网打尽之计。以至于辛卯之祸而惨矣。幸赖 先王圣明。曲加宽贷。使臣父获免鼎镬。生成之 恩。昊天罔极。及至壬辰之乱。 大驾西幸。臣父首蒙放赦之 命。圣旨有曰。知卿素有忠
夕之故耳。呜呼。臣父逮事 明 宣两朝。特蒙知遇。风云鱼水之驩。一时罕比。而徒以孤直之性。与人寡合。遇事敢言。不避忌讳。不幸中年。士论携贰。东西角立。而臣父尤被众攻。不能安于朝廷之上。及己丑逾变。臣父素为一边人所嫉。显有形迹之嫌。按狱之际。若不每人而救释。则毕竟怨毒。必皆丛于一身。是以。臣父逡巡辞避。初不欲担当。而臣父之友成浑时在坡山。劝起臣父曰。变生搢绅之间。将未免蔓延之患。若使他人主治此狱。则其不能以公心处于嫌疑也明矣。国事甚重。奚顾后虑。往复商确。出膺治鞫之 命。周旋伸理。多所平反。前后證左。明白如许。古人有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试将诸人被罪首末及臣父伸理曲折。参详舒究。则足见人言之不足信。而臣父之受厚诬也。大抵臣父枉被媒孽。为世祸首。众诽所归。人讳言之者。岂无所以然而然乎。盖由老奸当朝。乘机逞憾。上以欺蔽白日。下以笼络一世。为一网打尽之计。以至于辛卯之祸而惨矣。幸赖 先王圣明。曲加宽贷。使臣父获免鼎镬。生成之 恩。昊天罔极。及至壬辰之乱。 大驾西幸。臣父首蒙放赦之 命。圣旨有曰。知卿素有忠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3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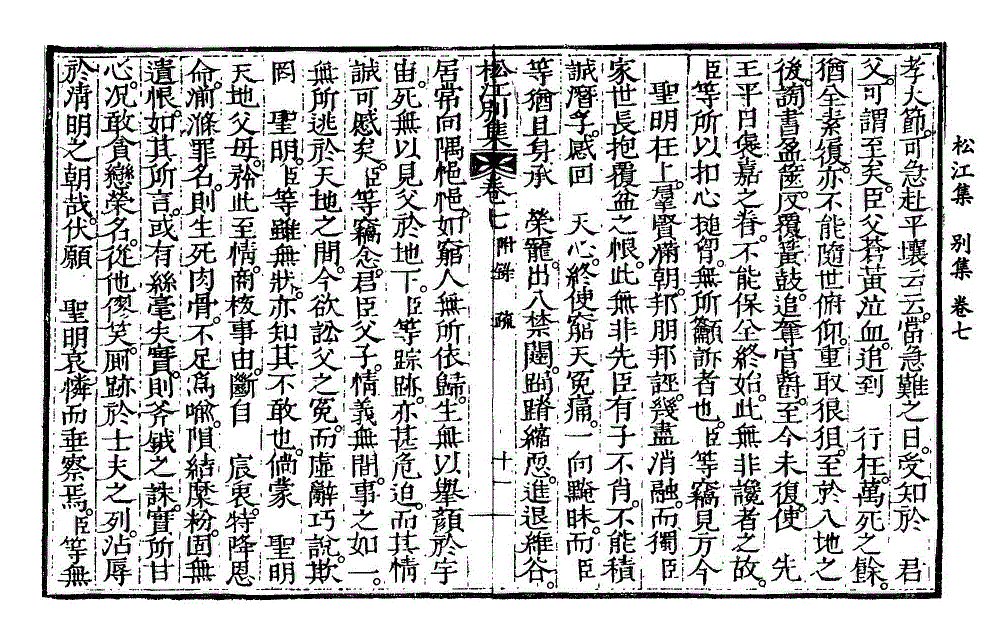 孝大节。可急赴平壤云云。当急难之日。受知于 君父。可谓至矣。臣父苍黄泣血。追到 行在。万死之馀。犹全素履。亦不能随世俯仰。重取狼狈。至于入地之后。谤书盈箧。反覆簧鼓。追夺官爵。至今未复。使 先王平日褒嘉之眷。不能保全终始。此无非谗者之故。臣等所以扣心搥胸。无所吁诉者也。臣等窃见方今 圣明在上。群贤满朝。邦朋邦诬。几尽消融。而独臣家世长抱覆盆之恨。此无非先臣有子不肖。不能积诚潜孚。感回 天心。终使穷天冤痛。一向黤昧。而臣等犹且身承 荣宠。出入禁闼。跼蹐缩恧。进退维谷。居常向隅悒悒。如穷人无所依归。生无以举颜于宇宙。死无以见父于地下。臣等踪迹。亦甚危迫。而其情诚可戚矣。臣等窃念。君臣父子。情义无间。事之如一。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今欲讼父之冤。而虚辞巧说。欺罔 圣明。臣等虽无状。亦知其不敢也。倘蒙 圣明天地父母。矜此至情。商核事由。断自 宸衷。特降恩命。湔涤罪名。则生死肉骨。不足为喻。陨结糜粉。固无遗恨。如其所言。或有丝毫失实。则斧钺之诛。实所甘心。况敢贪恋荣名。从他僇笑。厕迹于士夫之列。沾辱于清明之朝哉。伏愿 圣明哀怜而垂察焉。臣等无
孝大节。可急赴平壤云云。当急难之日。受知于 君父。可谓至矣。臣父苍黄泣血。追到 行在。万死之馀。犹全素履。亦不能随世俯仰。重取狼狈。至于入地之后。谤书盈箧。反覆簧鼓。追夺官爵。至今未复。使 先王平日褒嘉之眷。不能保全终始。此无非谗者之故。臣等所以扣心搥胸。无所吁诉者也。臣等窃见方今 圣明在上。群贤满朝。邦朋邦诬。几尽消融。而独臣家世长抱覆盆之恨。此无非先臣有子不肖。不能积诚潜孚。感回 天心。终使穷天冤痛。一向黤昧。而臣等犹且身承 荣宠。出入禁闼。跼蹐缩恧。进退维谷。居常向隅悒悒。如穷人无所依归。生无以举颜于宇宙。死无以见父于地下。臣等踪迹。亦甚危迫。而其情诚可戚矣。臣等窃念。君臣父子。情义无间。事之如一。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今欲讼父之冤。而虚辞巧说。欺罔 圣明。臣等虽无状。亦知其不敢也。倘蒙 圣明天地父母。矜此至情。商核事由。断自 宸衷。特降恩命。湔涤罪名。则生死肉骨。不足为喻。陨结糜粉。固无遗恨。如其所言。或有丝毫失实。则斧钺之诛。实所甘心。况敢贪恋荣名。从他僇笑。厕迹于士夫之列。沾辱于清明之朝哉。伏愿 圣明哀怜而垂察焉。臣等无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3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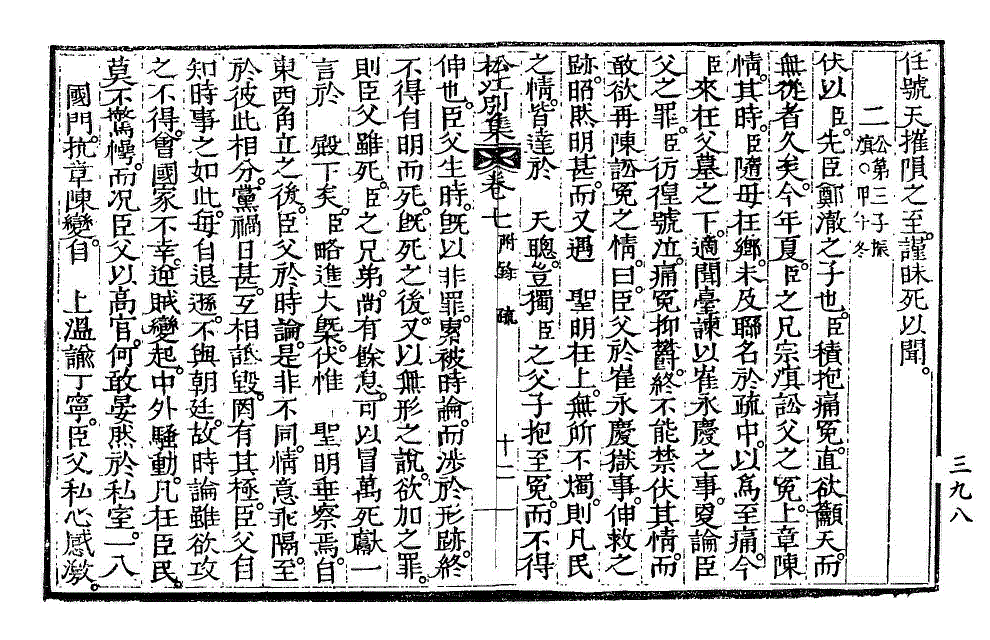 任号天摧陨之至。谨昧死以闻
任号天摧陨之至。谨昧死以闻伸冤疏(公第三子振溟○甲午冬)
伏以臣。先臣郑澈之子也。臣积抱痛冤。直欲吁天。而无从者久矣。今年夏。臣之兄宗溟讼父之冤。上章陈情。其时。臣随母在乡。未及联名于疏中。以为至痛。今臣来在父墓之下。适闻台谏以崔永庆之事。更论臣父之罪。臣彷徨号泣。痛冤抑郁。终不能禁伏其情。而敢欲再陈讼冤之情。曰。臣父于崔永庆狱事。伸救之迹。昭然明甚。而又遇 圣明在上。无所不烛。则凡民之情。皆达于 天聪。岂独臣之父子抱至冤。而不得伸也。臣父生时。既以非罪。累被时论。而涉于形迹。终不得自明而死。既死之后。又以无形之说。欲加之罪。则臣父虽死。臣之兄弟。尚有馀息。可以冒万死献一言于 殿下矣。臣略进大概。伏惟 圣明垂察焉。自东西角立之后。臣父于时论。是非不同。情意乖隔。至于彼此相分。党祸日甚。互相诋毁。罔有其极。臣父自知时事之如此。每自退逊。不与朝廷。故时论虽欲攻之不得。会国家不幸。逆贼变起。中外骚动。凡在臣民。莫不惊愕。而况臣父以高官。何敢晏然于私室。一入 国门。抗章陈变。自 上温谕丁宁。臣父私心感激。
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3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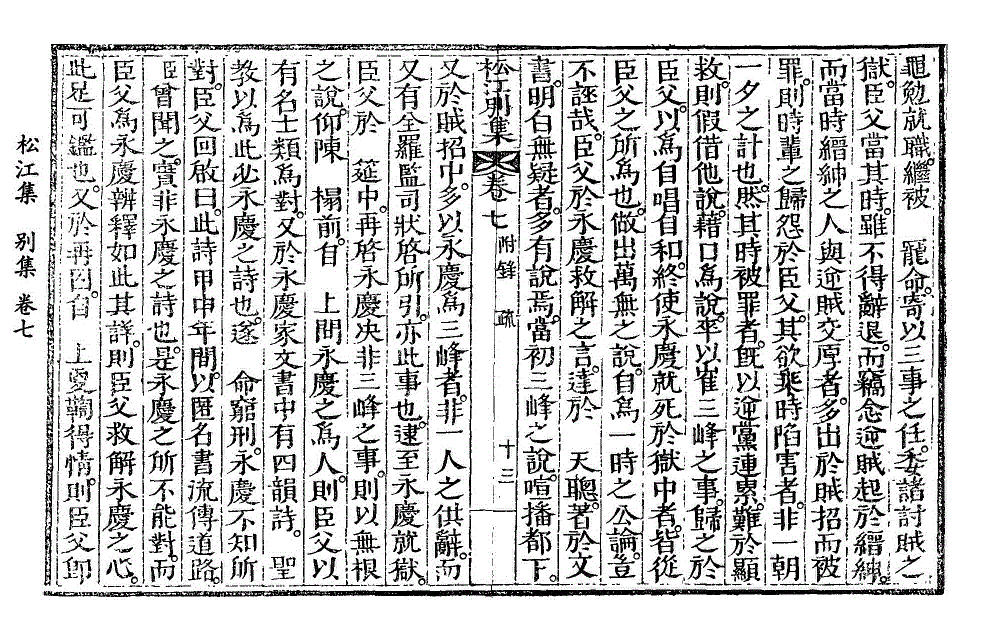 黾勉就职。继被 宠命。寄以三事之任。委诸讨贼之狱。臣父当其时。虽不得辞退。而窃念逆贼起于缙绅。而当时缙绅之人与逆贼交厚者。多出于贼招而被罪。则时辈之归怨于臣父。其欲乘时陷害者。非一朝一夕之计也。然其时被罪者。既以逆党连累。难于显救。则假借他说。藉口为说。卒以崔三峰之事。归之于臣父。以为自唱自和。终使永庆就死于狱中者。皆从臣父之所为也。做出万无之说。自为一时之公论。岂不诬哉。臣父于永庆救解之言。达于 天聪。著于文书。明白无疑者。多有说焉。当初三峰之说。喧播都下。又于贼招中。多以永庆为三峰者。非一人之供辞。而又有全罗监司状启所引。亦此事也。逮至永庆就狱。臣父于 筵中。再启永庆决非三峰之事。则以无根之说。仰陈 榻前。自 上问永庆之为人。则臣父以有名士类为对。又于永庆家文书中有四韵诗。 圣教以为此必永庆之诗也。遂 命穷刑。永庆不知所对。臣父回启曰。此诗甲申年间。以匿名书流传道路。臣曾闻之。实非永庆之诗也。是永庆之所不能对。而臣父为永庆辨释如此其详。则臣父救解永庆之心。此足可鉴也。又于再囚。自 上更鞫得情。则臣父即
黾勉就职。继被 宠命。寄以三事之任。委诸讨贼之狱。臣父当其时。虽不得辞退。而窃念逆贼起于缙绅。而当时缙绅之人与逆贼交厚者。多出于贼招而被罪。则时辈之归怨于臣父。其欲乘时陷害者。非一朝一夕之计也。然其时被罪者。既以逆党连累。难于显救。则假借他说。藉口为说。卒以崔三峰之事。归之于臣父。以为自唱自和。终使永庆就死于狱中者。皆从臣父之所为也。做出万无之说。自为一时之公论。岂不诬哉。臣父于永庆救解之言。达于 天聪。著于文书。明白无疑者。多有说焉。当初三峰之说。喧播都下。又于贼招中。多以永庆为三峰者。非一人之供辞。而又有全罗监司状启所引。亦此事也。逮至永庆就狱。臣父于 筵中。再启永庆决非三峰之事。则以无根之说。仰陈 榻前。自 上问永庆之为人。则臣父以有名士类为对。又于永庆家文书中有四韵诗。 圣教以为此必永庆之诗也。遂 命穷刑。永庆不知所对。臣父回启曰。此诗甲申年间。以匿名书流传道路。臣曾闻之。实非永庆之诗也。是永庆之所不能对。而臣父为永庆辨释如此其详。则臣父救解永庆之心。此足可鉴也。又于再囚。自 上更鞫得情。则臣父即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3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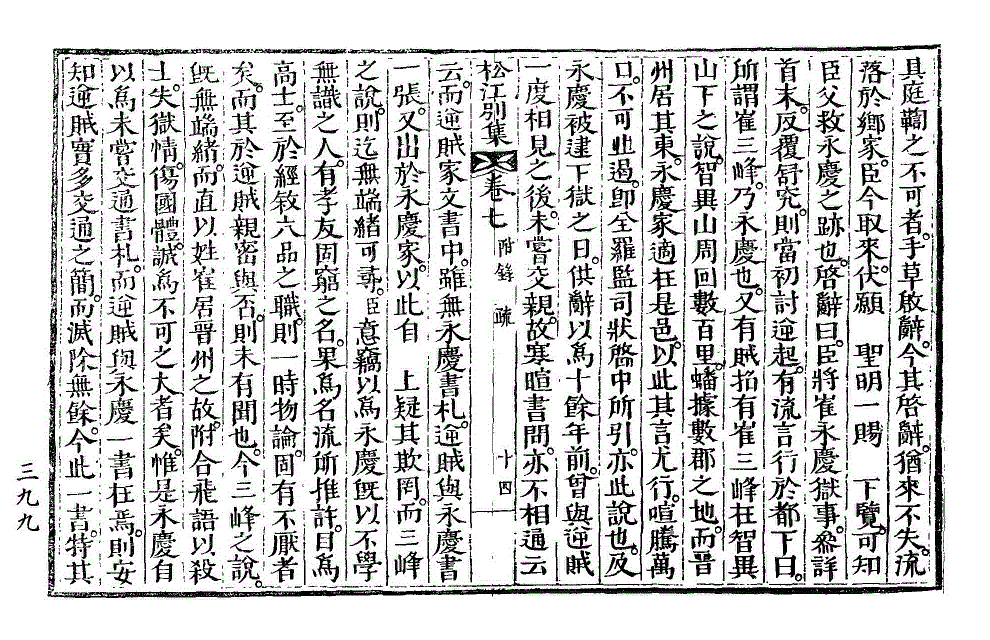 具庭鞫之不可者。手草启辞。今其启辞。犹来不失。流落于乡家。臣今取来。伏愿 圣明一赐 下览。可知臣父救永庆之迹也。启辞曰。臣将崔永庆狱事。参详首末。反覆舒究。则当初讨逆起。有流言行于都下曰。所谓崔三峰。乃永庆也。又有贼招有崔三峰在智异山下之说。智异山周回数百里。蟠据数郡之地。而晋州居其东。永庆家适在是邑。以此其言尤行。喧腾万口。不可止遏。即全罗监司状启中所引。亦此说也。及永庆被逮下狱之日。供辞以为十馀年前。曾与逆贼一度相见之后。未尝交亲。故寒暄书问。亦不相通云云。而逆贼家文书中。虽无永庆书札。逆贼与永庆书一张。又出于永庆家。以此自 上疑其欺罔。而三峰之说。则迄无端绪可寻。臣意窃以为永庆既以不学无识之人。有孝友固穷之名。果为名流所推许。目为高士。至于经叙六品之职。则一时物论。固有不厌者矣。而其于逆贼亲密与否。则未有闻也。今三峰之说。既无端绪。而直以姓崔居晋州之故。附合飞语以杀士。失狱情。伤国体。诚为不可之大者矣。惟是永庆自以为未尝交通书札。而逆贼与永庆一书在焉。则安知逆贼实多交通之简。而灭除无馀。今此一书。特其
具庭鞫之不可者。手草启辞。今其启辞。犹来不失。流落于乡家。臣今取来。伏愿 圣明一赐 下览。可知臣父救永庆之迹也。启辞曰。臣将崔永庆狱事。参详首末。反覆舒究。则当初讨逆起。有流言行于都下曰。所谓崔三峰。乃永庆也。又有贼招有崔三峰在智异山下之说。智异山周回数百里。蟠据数郡之地。而晋州居其东。永庆家适在是邑。以此其言尤行。喧腾万口。不可止遏。即全罗监司状启中所引。亦此说也。及永庆被逮下狱之日。供辞以为十馀年前。曾与逆贼一度相见之后。未尝交亲。故寒暄书问。亦不相通云云。而逆贼家文书中。虽无永庆书札。逆贼与永庆书一张。又出于永庆家。以此自 上疑其欺罔。而三峰之说。则迄无端绪可寻。臣意窃以为永庆既以不学无识之人。有孝友固穷之名。果为名流所推许。目为高士。至于经叙六品之职。则一时物论。固有不厌者矣。而其于逆贼亲密与否。则未有闻也。今三峰之说。既无端绪。而直以姓崔居晋州之故。附合飞语以杀士。失狱情。伤国体。诚为不可之大者矣。惟是永庆自以为未尝交通书札。而逆贼与永庆一书在焉。则安知逆贼实多交通之简。而灭除无馀。今此一书。特其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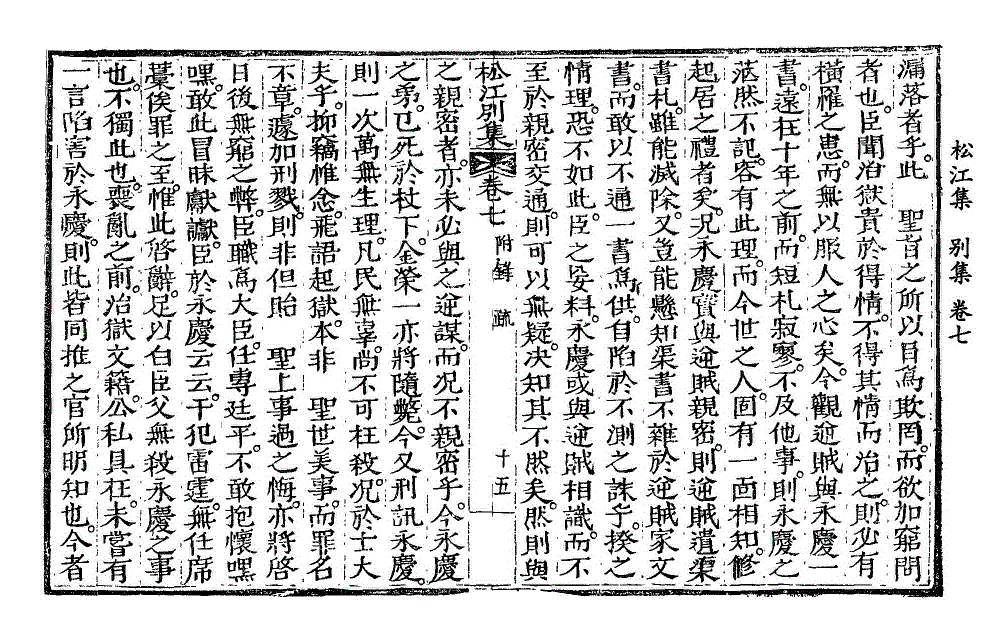 漏落者乎。此 圣旨之所以目为欺罔。而欲加穷问者也。臣闻治狱贵于得情。不得其情而治之。则必有横罹之患。而无以服人之心矣。今观逆贼与永庆一书。远在十年之前。而短札寂寥。不及他事。则永庆之茫然不记。容有此理。而今世之人。固有一面相知。修起居之礼者矣。况永庆实与逆贼亲密。则逆贼遗渠书札。虽能灭除。又岂能悬知渠书不杂于逆贼家文书。而敢以不通一书为供。自陷于不测之诛乎。揆之情理。恐不如此。臣之妄料。永庆或与逆贼相识。而不至于亲密交通。则可以无疑。决知其不然矣。然则与之亲密者。亦未必与之逆谋。而况不亲密乎。今永庆之弟。已死于杖下。金荣一亦将随毙。今又刑讯永庆。则一次万无生理。凡民无辜。尚不可枉杀。况于士大夫乎。抑窃惟念。飞语起狱。本非 圣世美事。而罪名不章。遽加刑戮。则非但贻 圣上事过之悔。亦将启日后无穷之弊。臣职为大臣。任专廷平。不敢抱怀默默。敢此冒昧献谳。臣于永庆云云。干犯雷霆。无任席藁俟罪之至。惟此启辞。足以白臣父无杀永庆之事也。不独此也。丧乱之前。治狱文籍。公私具在。未尝有一言陷害于永庆。则此皆同推之官所明知也。今者
漏落者乎。此 圣旨之所以目为欺罔。而欲加穷问者也。臣闻治狱贵于得情。不得其情而治之。则必有横罹之患。而无以服人之心矣。今观逆贼与永庆一书。远在十年之前。而短札寂寥。不及他事。则永庆之茫然不记。容有此理。而今世之人。固有一面相知。修起居之礼者矣。况永庆实与逆贼亲密。则逆贼遗渠书札。虽能灭除。又岂能悬知渠书不杂于逆贼家文书。而敢以不通一书为供。自陷于不测之诛乎。揆之情理。恐不如此。臣之妄料。永庆或与逆贼相识。而不至于亲密交通。则可以无疑。决知其不然矣。然则与之亲密者。亦未必与之逆谋。而况不亲密乎。今永庆之弟。已死于杖下。金荣一亦将随毙。今又刑讯永庆。则一次万无生理。凡民无辜。尚不可枉杀。况于士大夫乎。抑窃惟念。飞语起狱。本非 圣世美事。而罪名不章。遽加刑戮。则非但贻 圣上事过之悔。亦将启日后无穷之弊。臣职为大臣。任专廷平。不敢抱怀默默。敢此冒昧献谳。臣于永庆云云。干犯雷霆。无任席藁俟罪之至。惟此启辞。足以白臣父无杀永庆之事也。不独此也。丧乱之前。治狱文籍。公私具在。未尝有一言陷害于永庆。则此皆同推之官所明知也。今者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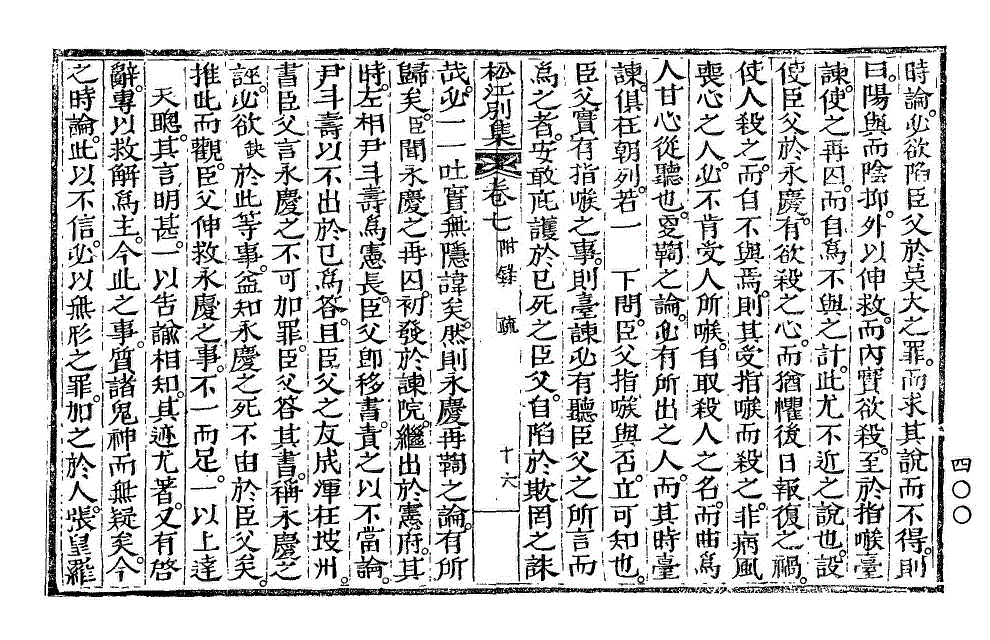 时论。必欲陷臣父于莫大之罪。而求其说而不得。则曰。阳与而阴抑。外以伸救。而内实欲杀。至于指嗾台谏。使之再囚。而自为不与之计。此尤不近之说也。设使臣父于永庆。有欲杀之心。而犹惧后日报复之祸。使人杀之。而自不与焉。则其受指嗾而杀之。非病风丧心之人。必不肯受人所嗾。自取杀人之名。而曲为人甘心从听也。更鞫之论。必有所出之人。而其时台谏。俱在朝列。若一 下问。臣父指嗾与否。立可知也。臣父实有指嗾之事。则台谏必有听臣父之所言而为之者。安敢庇护于已死之臣父。自陷于欺罔之诛哉。必一一吐实无隐讳矣。然则永庆再鞫之论。有所归矣。臣闻永庆之再囚。初发于谏院。继出于宪府。其时。左相尹斗寿为宪长。臣父即移书。责之以不当论。尹斗寿以不出于己为答。且臣父之友成浑在坡州。书臣父言永庆之不可加罪。臣父答其书。称永庆之诬。必欲(缺)于此等事。益知永庆之死不由于臣父矣。推此而观。臣父伸救永庆之事。不一而足。一以上达 天聪。其言明甚。一以告谕相知。其迹尤著。又有启辞。专以救解为主。今此之事。质诸鬼神而无疑矣。今之时论。此以不信。必以无形之罪。加之于人。张皇罗
时论。必欲陷臣父于莫大之罪。而求其说而不得。则曰。阳与而阴抑。外以伸救。而内实欲杀。至于指嗾台谏。使之再囚。而自为不与之计。此尤不近之说也。设使臣父于永庆。有欲杀之心。而犹惧后日报复之祸。使人杀之。而自不与焉。则其受指嗾而杀之。非病风丧心之人。必不肯受人所嗾。自取杀人之名。而曲为人甘心从听也。更鞫之论。必有所出之人。而其时台谏。俱在朝列。若一 下问。臣父指嗾与否。立可知也。臣父实有指嗾之事。则台谏必有听臣父之所言而为之者。安敢庇护于已死之臣父。自陷于欺罔之诛哉。必一一吐实无隐讳矣。然则永庆再鞫之论。有所归矣。臣闻永庆之再囚。初发于谏院。继出于宪府。其时。左相尹斗寿为宪长。臣父即移书。责之以不当论。尹斗寿以不出于己为答。且臣父之友成浑在坡州。书臣父言永庆之不可加罪。臣父答其书。称永庆之诬。必欲(缺)于此等事。益知永庆之死不由于臣父矣。推此而观。臣父伸救永庆之事。不一而足。一以上达 天聪。其言明甚。一以告谕相知。其迹尤著。又有启辞。专以救解为主。今此之事。质诸鬼神而无疑矣。今之时论。此以不信。必以无形之罪。加之于人。张皇罗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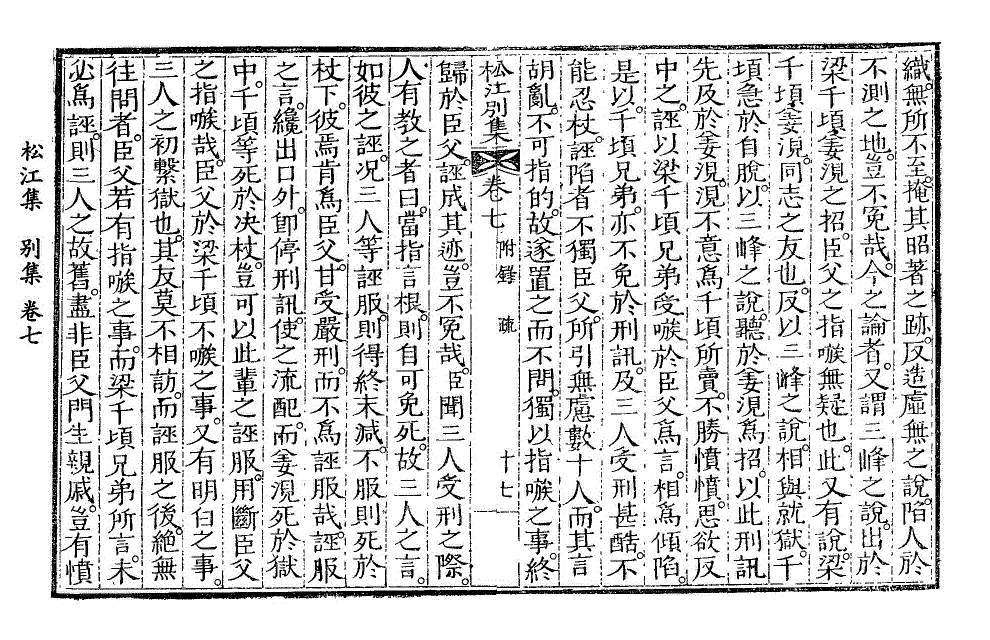 织。无所不至。掩其昭著之迹。反造虚无之说。陷人于不测之地。岂不冤哉。今之论者。又谓三峰之说。出于梁千顷,姜涀之招。臣父之指嗾无疑也。此又有说。梁千顷,姜涀。同志之友也。反以三峰之说。相与就狱。千顷急于自脱。以三峰之说。听于姜涀为招。以此刑讯先及于姜涀。涀不意为千顷所卖。不胜愤愤。思欲反中之。诬以梁千顷兄弟受嗾于臣父为言。相为倾陷。是以。千顷兄弟。亦不免于刑讯。及三人受刑甚酷。不能忍杖。诬陷者不独臣父。所引无虑数十人。而其言胡乱。不可指的。故遂置之而不问。独以指嗾之事。终归于臣父。诬成其迹。岂不冤哉。臣闻三人受刑之际。人有教之者曰。当指言根。则自可免死。故三人之言。如彼之诬。况三人等诬服。则得终末减。不服则死于杖下。彼焉肯为臣父。甘受严刑。而不为诬服哉。诬服之言。才出口外。即停刑讯。使之流配。而姜涀死于狱中。千顷等死于决杖。岂可以此辈之诬服。用断臣父之指嗾哉。臣父于梁千顷不嗾之事。又有明白之事。三人之初系狱也。其友莫不相访。而诬服之后。绝无往问者。臣父若有指嗾之事。而梁千顷兄弟所言。未必为诬。则三人之故旧。尽非臣父门生亲戚。岂有愤
织。无所不至。掩其昭著之迹。反造虚无之说。陷人于不测之地。岂不冤哉。今之论者。又谓三峰之说。出于梁千顷,姜涀之招。臣父之指嗾无疑也。此又有说。梁千顷,姜涀。同志之友也。反以三峰之说。相与就狱。千顷急于自脱。以三峰之说。听于姜涀为招。以此刑讯先及于姜涀。涀不意为千顷所卖。不胜愤愤。思欲反中之。诬以梁千顷兄弟受嗾于臣父为言。相为倾陷。是以。千顷兄弟。亦不免于刑讯。及三人受刑甚酷。不能忍杖。诬陷者不独臣父。所引无虑数十人。而其言胡乱。不可指的。故遂置之而不问。独以指嗾之事。终归于臣父。诬成其迹。岂不冤哉。臣闻三人受刑之际。人有教之者曰。当指言根。则自可免死。故三人之言。如彼之诬。况三人等诬服。则得终末减。不服则死于杖下。彼焉肯为臣父。甘受严刑。而不为诬服哉。诬服之言。才出口外。即停刑讯。使之流配。而姜涀死于狱中。千顷等死于决杖。岂可以此辈之诬服。用断臣父之指嗾哉。臣父于梁千顷不嗾之事。又有明白之事。三人之初系狱也。其友莫不相访。而诬服之后。绝无往问者。臣父若有指嗾之事。而梁千顷兄弟所言。未必为诬。则三人之故旧。尽非臣父门生亲戚。岂有愤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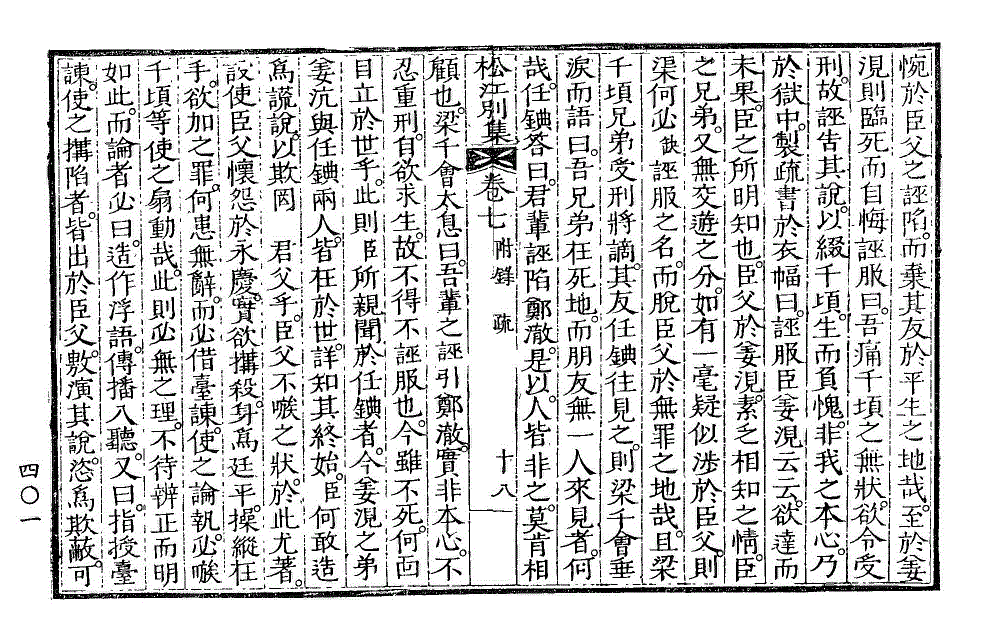 惋于臣父之诬陷。而弃其友于平生之地哉。至于姜涀则临死而自悔诬服曰。吾痛千顷之无状。欲令受刑。故诬告其说。以缀千顷。生而负愧。非我之本心。乃于狱中。制疏书于衣幅曰。诬服臣姜涀云云。欲达而未果。臣之所明知也。臣父于姜涀。素乏相知之情。臣之兄弟。又无交游之分。如有一毫疑似涉于臣父。则渠何必(缺)诬服之名。而脱臣父于无罪之地哉。且梁千顷兄弟受刑将谪。其友任錪往见之。则梁千会垂泪而语曰。吾兄弟在死地。而朋友无一人来见者。何哉。任錪答曰。君辈诬陷郑澈。是以。人皆非之。莫肯相顾也。梁千会太息曰。吾辈之诬引郑澈。实非本心。不忍重刑。自欲求生。故不得不诬服也。今虽不死。何面目立于世乎。此则臣所亲闻于任錪者。今姜涀之弟姜沆与任錪两人。皆在于世。详知其终始。臣何敢造为谎说。以欺罔 君父乎。臣父不嗾之状。于此尤著。设使臣父怀怨于永庆。实欲搆杀。身为廷平。操纵在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必借台谏。使之论执。必嗾千顷等使之扇动哉。此则必无之理。不待辨正而明如此。而论者必曰。造作浮语。传播入听。又曰。指授台谏。使之搆陷者。皆出于臣父。敷演其说。恣为欺蔽。可
惋于臣父之诬陷。而弃其友于平生之地哉。至于姜涀则临死而自悔诬服曰。吾痛千顷之无状。欲令受刑。故诬告其说。以缀千顷。生而负愧。非我之本心。乃于狱中。制疏书于衣幅曰。诬服臣姜涀云云。欲达而未果。臣之所明知也。臣父于姜涀。素乏相知之情。臣之兄弟。又无交游之分。如有一毫疑似涉于臣父。则渠何必(缺)诬服之名。而脱臣父于无罪之地哉。且梁千顷兄弟受刑将谪。其友任錪往见之。则梁千会垂泪而语曰。吾兄弟在死地。而朋友无一人来见者。何哉。任錪答曰。君辈诬陷郑澈。是以。人皆非之。莫肯相顾也。梁千会太息曰。吾辈之诬引郑澈。实非本心。不忍重刑。自欲求生。故不得不诬服也。今虽不死。何面目立于世乎。此则臣所亲闻于任錪者。今姜涀之弟姜沆与任錪两人。皆在于世。详知其终始。臣何敢造为谎说。以欺罔 君父乎。臣父不嗾之状。于此尤著。设使臣父怀怨于永庆。实欲搆杀。身为廷平。操纵在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必借台谏。使之论执。必嗾千顷等使之扇动哉。此则必无之理。不待辨正而明如此。而论者必曰。造作浮语。传播入听。又曰。指授台谏。使之搆陷者。皆出于臣父。敷演其说。恣为欺蔽。可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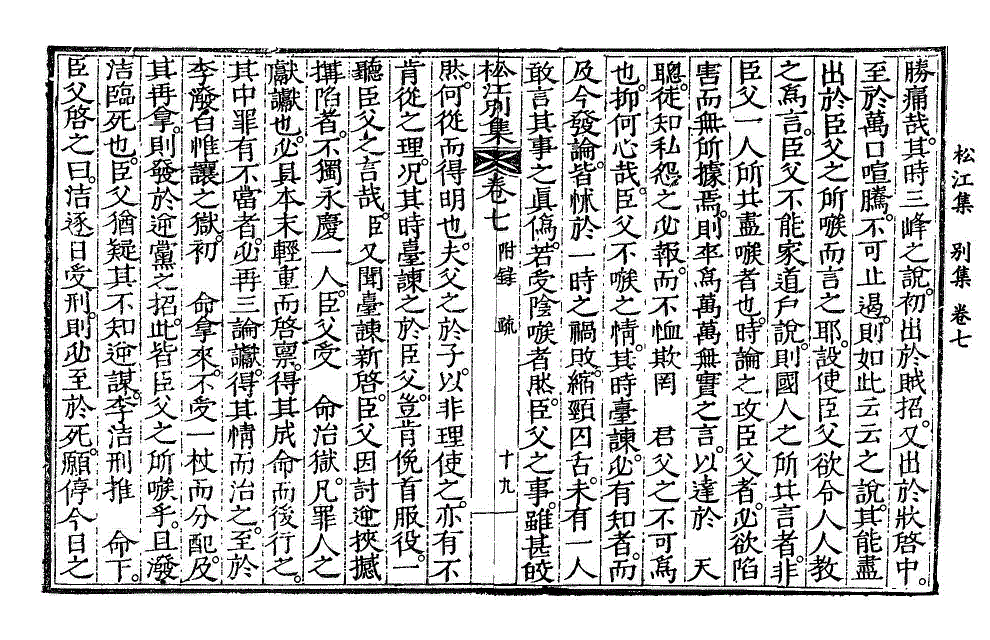 胜痛哉。其时三峰之说。初出于贼招。又出于状启中。至于万口喧腾。不可止遏。则如此云云之说。其能尽出于臣父之所嗾而言之耶。设使臣父欲令人人教之为言。臣父不能家道户说。则国人之所共言者。非臣父一人所共尽嗾者也。时论之攻臣父者。必欲陷害而无所据焉。则卒为万万无实之言。以达于 天聪。徒知私怨之必报。而不恤欺罔 君父之不可为也。抑何心哉。臣父不嗾之情。其时台谏。必有知者。而及今发论。皆怵于一时之祸败。缩颈囚舌。未有一人敢言其事之真伪。若受阴嗾者然。臣父之事。虽甚皎然。何从而得明也。夫父之于子。以非理使之。亦有不肯从之理。况其时台谏之于臣父。岂肯俛首服役。一听臣父之言哉。臣又闻台谏新启。臣父因讨逆挟撼搆陷者。不独永庆一人。臣父受 命治狱。凡罪人之献谳也。必具本末轻重而启禀。得其成命而后行之。其中罪有不当者。必再三论谳。得其情而治之。至于李泼,白惟让之狱。初 命拿来。不受一杖而分配。及其再拿。则发于逆党之招。此皆臣父之所嗾乎。且泼,洁临死也。臣父犹疑其不知逆谋。李洁刑推 命下。臣父启之曰。洁逐日受刑。则必至于死。愿停今日之
胜痛哉。其时三峰之说。初出于贼招。又出于状启中。至于万口喧腾。不可止遏。则如此云云之说。其能尽出于臣父之所嗾而言之耶。设使臣父欲令人人教之为言。臣父不能家道户说。则国人之所共言者。非臣父一人所共尽嗾者也。时论之攻臣父者。必欲陷害而无所据焉。则卒为万万无实之言。以达于 天聪。徒知私怨之必报。而不恤欺罔 君父之不可为也。抑何心哉。臣父不嗾之情。其时台谏。必有知者。而及今发论。皆怵于一时之祸败。缩颈囚舌。未有一人敢言其事之真伪。若受阴嗾者然。臣父之事。虽甚皎然。何从而得明也。夫父之于子。以非理使之。亦有不肯从之理。况其时台谏之于臣父。岂肯俛首服役。一听臣父之言哉。臣又闻台谏新启。臣父因讨逆挟撼搆陷者。不独永庆一人。臣父受 命治狱。凡罪人之献谳也。必具本末轻重而启禀。得其成命而后行之。其中罪有不当者。必再三论谳。得其情而治之。至于李泼,白惟让之狱。初 命拿来。不受一杖而分配。及其再拿。则发于逆党之招。此皆臣父之所嗾乎。且泼,洁临死也。臣父犹疑其不知逆谋。李洁刑推 命下。臣父启之曰。洁逐日受刑。则必至于死。愿停今日之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02L 页
 刑。以此 天威震赫。以专辄 下教。当时傍观者。皆为臣父危之。以此一事。足以见臣父不杀之心也。夫人之善恶。行事易(缺)著明。今之论者曰。阳救阴害。阳者易知。而阴者难卞。舍易知之实迹。而取难卞之虚说。以此决人之罪。而果能服人之心乎。汉之颜异。以腹诽而受诛。宋之岳飞。以莫须有而就戮。此前史之所非也。臣父之今日其受罪之黯暗。不幸而相近。则岂非痛冤之甚乎。呜呼。臣父本以孤危之踪。不合于时论。每辞爵禄。自拟终老于林壑。遭遇国乱。当事未久。祸胎重发。几不能免。幸赖 圣明在上。得免重戮。 天恩罔极。感泣何言。今臣父已死。又被非罪。而抱冤于泉下。则死亦不暝目矣。臣以草土微喘。敢抗封章。极知僭越。罪不容诛。臣生不能讼父之冤。死无以见父于地下。故不避鈇钺。敢此陈达。伏愿 圣明垂察哀悰。 特赐进览。臣之父子之冤。庶几自明于天日之下。臣虽伏鈇锧而死。万万无所恨矣。情溢辞蹙。不知所裁。臣无任号天痛哭之至。谨昧死以闻。
刑。以此 天威震赫。以专辄 下教。当时傍观者。皆为臣父危之。以此一事。足以见臣父不杀之心也。夫人之善恶。行事易(缺)著明。今之论者曰。阳救阴害。阳者易知。而阴者难卞。舍易知之实迹。而取难卞之虚说。以此决人之罪。而果能服人之心乎。汉之颜异。以腹诽而受诛。宋之岳飞。以莫须有而就戮。此前史之所非也。臣父之今日其受罪之黯暗。不幸而相近。则岂非痛冤之甚乎。呜呼。臣父本以孤危之踪。不合于时论。每辞爵禄。自拟终老于林壑。遭遇国乱。当事未久。祸胎重发。几不能免。幸赖 圣明在上。得免重戮。 天恩罔极。感泣何言。今臣父已死。又被非罪。而抱冤于泉下。则死亦不暝目矣。臣以草土微喘。敢抗封章。极知僭越。罪不容诛。臣生不能讼父之冤。死无以见父于地下。故不避鈇钺。敢此陈达。伏愿 圣明垂察哀悰。 特赐进览。臣之父子之冤。庶几自明于天日之下。臣虽伏鈇锧而死。万万无所恨矣。情溢辞蹙。不知所裁。臣无任号天痛哭之至。谨昧死以闻。畸庵答李潜窝(命俊)书
今世之事。吾兄既已自知而自悲之矣。如仆复何言哉。抑又念人心贸贸。惟利是急。势之所在。则趋之如
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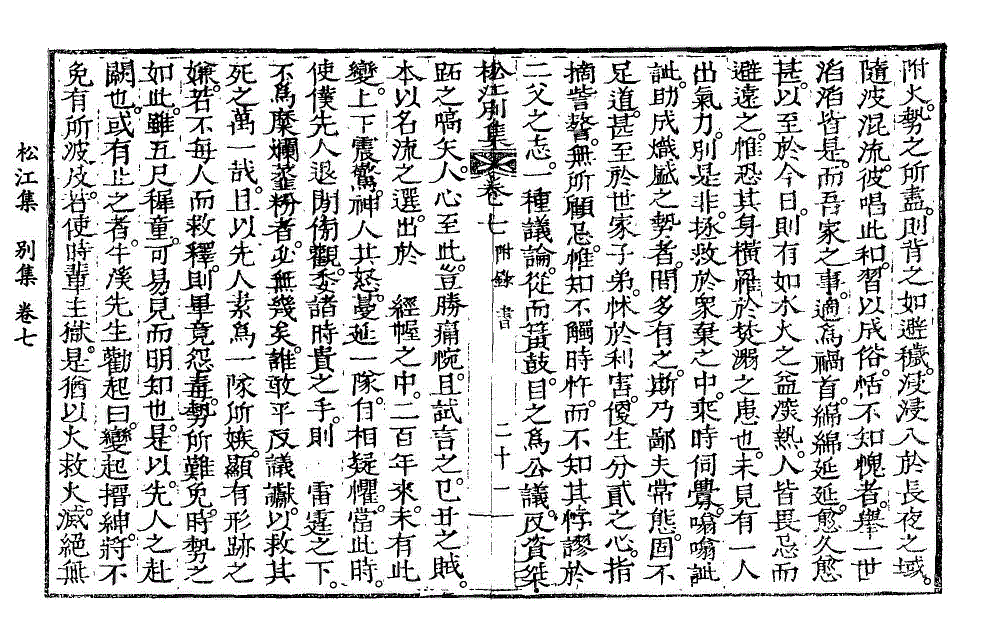 附火。势之所尽。则背之如避秽。浸浸入于长夜之域。随波混流。彼唱此和。习以成俗。恬不知愧者。举一世滔滔皆是。而吾家之事。适为祸首。绵绵延延。愈久愈甚。以至于今日。则有如水火之益深热。人皆畏忌而避远之。惟恐其身横罹于焚溺之患也。未见有一人出气力。别是非。拯救于众弃之中。乘时伺衅。噏噏訾訾。助成炽盛之势者。间多有之。斯乃鄙夫常态。固不足道。甚至于世家子弟。怵于利害。便生分贰之心。指摘訾謷。无所顾忌。惟知不触时忤。而不知其悖谬于二父之志。一种议论。从而簧鼓。目之为公议。反资桀,蹠之嗃矢。人心至此。岂胜痛惋。且试言之。己丑之贼。本以名流之选。出于 经幄之中。二百年来。未有此变。上下震惊。神人共怒。蔓延一队。自相疑惧。当此时。使仆先人退閒傍观。委诸时贵之手。则 雷霆之下。不为糜烂齑粉者。必无几矣。谁敢平反议谳。以救其死之万一哉。且以先人素为一队所嫉。显有形迹之嫌。若不每人而救释。则毕竟怨毒。势所难免。时势之如此。虽五尺稚童。可易见而明知也。是以。先人之赴阙也。或有止之者。牛溪先生劝起曰。变起搢绅。将不免有所波及。若使时辈主狱。是犹以火救火。灭减绝无
附火。势之所尽。则背之如避秽。浸浸入于长夜之域。随波混流。彼唱此和。习以成俗。恬不知愧者。举一世滔滔皆是。而吾家之事。适为祸首。绵绵延延。愈久愈甚。以至于今日。则有如水火之益深热。人皆畏忌而避远之。惟恐其身横罹于焚溺之患也。未见有一人出气力。别是非。拯救于众弃之中。乘时伺衅。噏噏訾訾。助成炽盛之势者。间多有之。斯乃鄙夫常态。固不足道。甚至于世家子弟。怵于利害。便生分贰之心。指摘訾謷。无所顾忌。惟知不触时忤。而不知其悖谬于二父之志。一种议论。从而簧鼓。目之为公议。反资桀,蹠之嗃矢。人心至此。岂胜痛惋。且试言之。己丑之贼。本以名流之选。出于 经幄之中。二百年来。未有此变。上下震惊。神人共怒。蔓延一队。自相疑惧。当此时。使仆先人退閒傍观。委诸时贵之手。则 雷霆之下。不为糜烂齑粉者。必无几矣。谁敢平反议谳。以救其死之万一哉。且以先人素为一队所嫉。显有形迹之嫌。若不每人而救释。则毕竟怨毒。势所难免。时势之如此。虽五尺稚童。可易见而明知也。是以。先人之赴阙也。或有止之者。牛溪先生劝起曰。变起搢绅。将不免有所波及。若使时辈主狱。是犹以火救火。灭减绝无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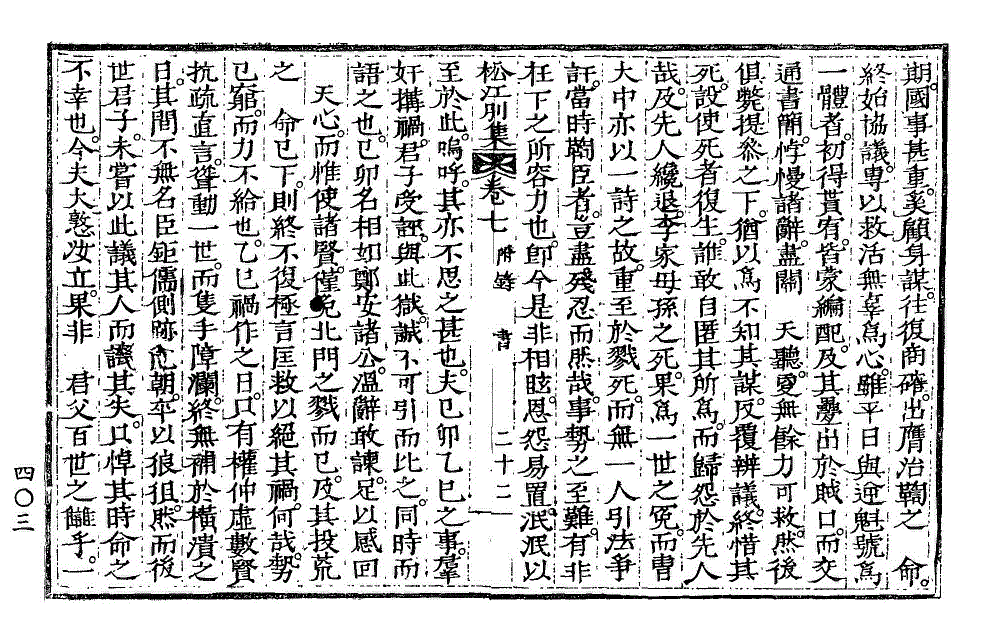 期。国事甚重。奚顾身谋。往复商确。出膺治鞫之 命。终始协议。专以救活无辜为心。虽平日与逆魁号为一体者。初得贳宥。皆蒙编配。及其叠出于贼口。而交通书简。悖慢诸辞。尽关 天听。更无馀力可救。然后俱毙提参之下。犹以为不知其谋。反覆辨议。终惜其死。设使死者复生。谁敢自匿其所为。而归怨于先人哉。及先人才退。李家母孙之死。果为一世之冤。而曹大中亦以一诗之故。重至于戮死。而无一人引法争讦。当时鞫臣者。岂尽残忍而然哉。事势之至难。有非在下之所容力也。即今是非相眩。恩怨易置。泯泯以至于此。呜呼。其亦不思之甚也。夫己卯乙巳之事。群奸搆祸。君子受诬。与此狱。诚不可引而比之。同时而语之也。己卯名相如郑安诸公。温辞敢谏。足以感回 天心。而惟使诸贤。仅免北门之戮而已。及其投荒之 命已下。则终不复极言匡救以绝其祸。何哉。势已穷。而力不给也。乙巳祸作之日。只有权仲虚数贤抗疏直言。耸动一世。而只手障澜。终无补于横溃之日。其间不无名臣钜儒侧迹危朝。卒以狼狈。然而后世君子。未尝以此议其人而讥其失。只悼其时命之不幸也。今夫大憝汝立。果非 君父百世之雠乎。一
期。国事甚重。奚顾身谋。往复商确。出膺治鞫之 命。终始协议。专以救活无辜为心。虽平日与逆魁号为一体者。初得贳宥。皆蒙编配。及其叠出于贼口。而交通书简。悖慢诸辞。尽关 天听。更无馀力可救。然后俱毙提参之下。犹以为不知其谋。反覆辨议。终惜其死。设使死者复生。谁敢自匿其所为。而归怨于先人哉。及先人才退。李家母孙之死。果为一世之冤。而曹大中亦以一诗之故。重至于戮死。而无一人引法争讦。当时鞫臣者。岂尽残忍而然哉。事势之至难。有非在下之所容力也。即今是非相眩。恩怨易置。泯泯以至于此。呜呼。其亦不思之甚也。夫己卯乙巳之事。群奸搆祸。君子受诬。与此狱。诚不可引而比之。同时而语之也。己卯名相如郑安诸公。温辞敢谏。足以感回 天心。而惟使诸贤。仅免北门之戮而已。及其投荒之 命已下。则终不复极言匡救以绝其祸。何哉。势已穷。而力不给也。乙巳祸作之日。只有权仲虚数贤抗疏直言。耸动一世。而只手障澜。终无补于横溃之日。其间不无名臣钜儒侧迹危朝。卒以狼狈。然而后世君子。未尝以此议其人而讥其失。只悼其时命之不幸也。今夫大憝汝立。果非 君父百世之雠乎。一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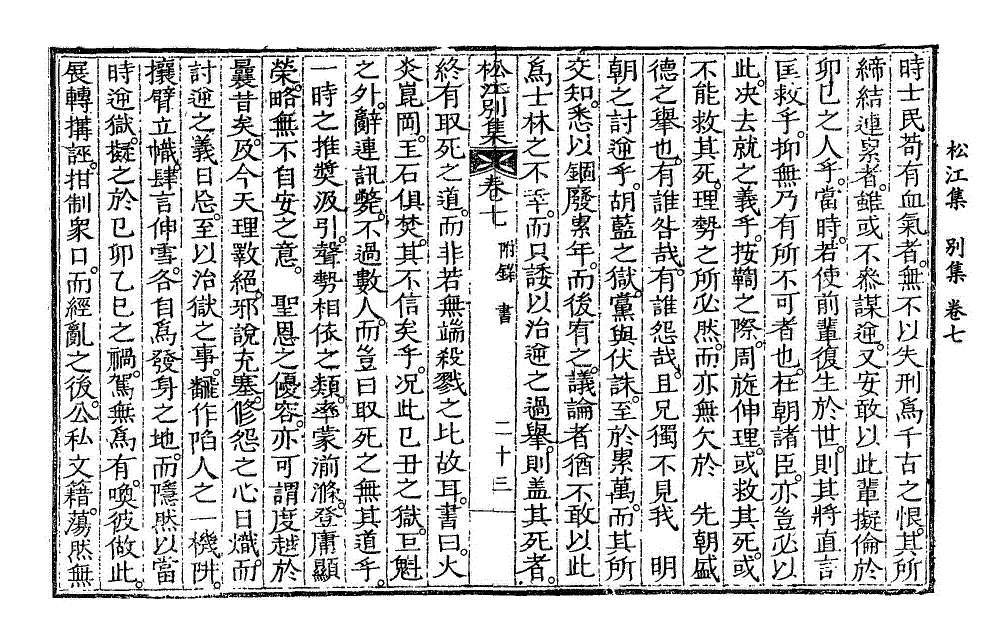 时士民苟有血气者。无不以失刑为千古之恨。其所缔结连累者。虽或不参谋逆。又安敢以此辈拟伦于卯,巳之人乎。当时。若使前辈复生于世。则其将直言匡救乎。抑无乃有所不可者也。在朝诸臣。亦岂必以此。决去就之义乎。按鞫之际。周旋伸理。或救其死。或不能救其死。理势之所必然。而亦无欠于 先朝盛德之举也。有谁咎哉。有谁怨哉。且兄独不见我 明朝之讨逆乎。胡蓝之狱。党与伏诛。至于累万。而其所交知。悉以锢废累年。而后宥之。议论者犹不敢以此为士林之不幸。而只诿以治逆之过举。则盖其死者。终有取死之道。而非若无端杀戮之比故耳。书曰。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其不信矣乎。况此己丑之狱。巨魁之外。辞连讯毙。不过数人。而岂曰取死之无其道乎。一时之推奖汲引。声势相依之类。率蒙湔涤。登庸显荣。略无不自安之意。 圣恩之优容。亦可谓度越于曩昔矣。及今天理斁绝。邪说充塞。修怨之心日炽。而讨逆之义日忘。至以治狱之事。翻作陷人之一机阱。攘臂立帜。肆言伸雪。各自为发身之地。而隐然以当时逆狱。拟之于己卯乙巳之祸。驾无为有。唤彼做此。展转搆诬。钳制众口。而经乱之后。公私文籍。荡然无
时士民苟有血气者。无不以失刑为千古之恨。其所缔结连累者。虽或不参谋逆。又安敢以此辈拟伦于卯,巳之人乎。当时。若使前辈复生于世。则其将直言匡救乎。抑无乃有所不可者也。在朝诸臣。亦岂必以此。决去就之义乎。按鞫之际。周旋伸理。或救其死。或不能救其死。理势之所必然。而亦无欠于 先朝盛德之举也。有谁咎哉。有谁怨哉。且兄独不见我 明朝之讨逆乎。胡蓝之狱。党与伏诛。至于累万。而其所交知。悉以锢废累年。而后宥之。议论者犹不敢以此为士林之不幸。而只诿以治逆之过举。则盖其死者。终有取死之道。而非若无端杀戮之比故耳。书曰。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其不信矣乎。况此己丑之狱。巨魁之外。辞连讯毙。不过数人。而岂曰取死之无其道乎。一时之推奖汲引。声势相依之类。率蒙湔涤。登庸显荣。略无不自安之意。 圣恩之优容。亦可谓度越于曩昔矣。及今天理斁绝。邪说充塞。修怨之心日炽。而讨逆之义日忘。至以治狱之事。翻作陷人之一机阱。攘臂立帜。肆言伸雪。各自为发身之地。而隐然以当时逆狱。拟之于己卯乙巳之祸。驾无为有。唤彼做此。展转搆诬。钳制众口。而经乱之后。公私文籍。荡然无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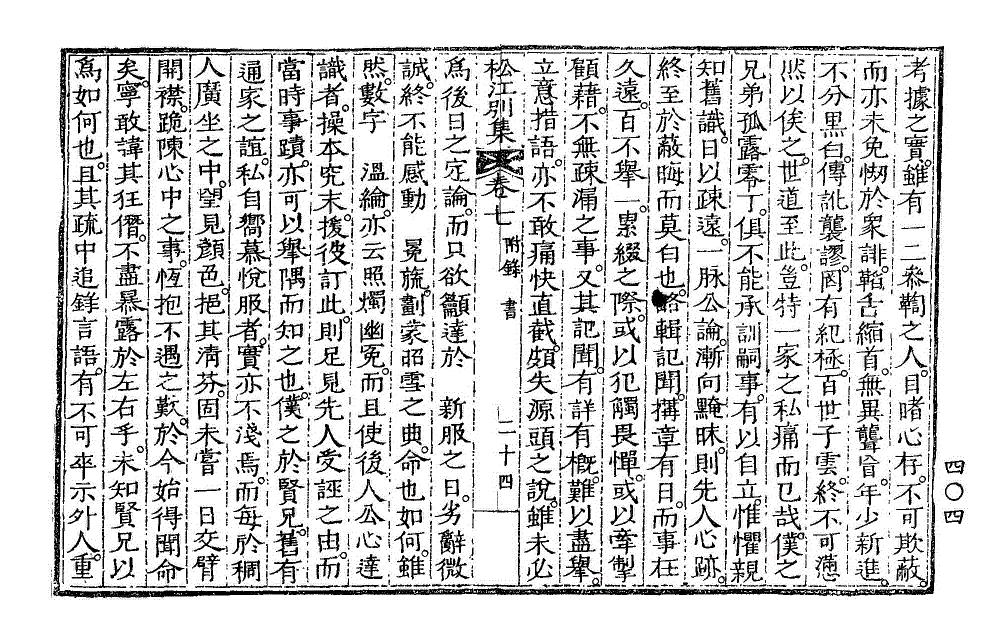 考据之实。虽有一二参鞫之人。目睹心存。不可欺蔽。而亦未免怯于众诽。韬舌缩首。无异聋盲。年少新进。不分黑白。传讹袭谬。罔有纪极。百世子云。终不可懑然以俟之。世道至此。岂特一家之私痛而已哉。仆之兄弟孤露零丁。俱不能承训嗣事。有以自立。惟惧亲知旧识。日以疏远。一脉公论。渐向黤昧。则先人心迹。终至于蔽晦而莫白也。略辑记闻。搆章有日。而事在久远。百不举一。累缀之际。或以犯触畏惮。或以牵掣顾藉。不无疏漏之事。又其记闻。有详有概。难以尽举。立意措语。亦不敢痛快直截。颇失源头之说。虽未必为后日之定论。而只欲吁达于 新服之日。劣辞微诚。终不能感动 冕旒。划蒙昭雪之典。命也如何。虽然。数字 温纶。亦云照烛幽冤。而且使后人公心达识者。操本究末。援彼订此。则足见先人受诬之由。而当时事迹。亦可以举隅而知之也。仆之于贤兄。旧有通家之谊。私自向慕悦服者。实亦不浅焉。而每于稠人广坐之中。望见颜色。挹其清芬。固未尝一日交臂开襟。跪陈心中之事。恒抱不遇之叹。于今始得闻命矣。宁敢讳其狂僭。不尽暴露于左右乎。未知贤兄以为如何也。且其疏中追录言语。有不可卒示外人。重
考据之实。虽有一二参鞫之人。目睹心存。不可欺蔽。而亦未免怯于众诽。韬舌缩首。无异聋盲。年少新进。不分黑白。传讹袭谬。罔有纪极。百世子云。终不可懑然以俟之。世道至此。岂特一家之私痛而已哉。仆之兄弟孤露零丁。俱不能承训嗣事。有以自立。惟惧亲知旧识。日以疏远。一脉公论。渐向黤昧。则先人心迹。终至于蔽晦而莫白也。略辑记闻。搆章有日。而事在久远。百不举一。累缀之际。或以犯触畏惮。或以牵掣顾藉。不无疏漏之事。又其记闻。有详有概。难以尽举。立意措语。亦不敢痛快直截。颇失源头之说。虽未必为后日之定论。而只欲吁达于 新服之日。劣辞微诚。终不能感动 冕旒。划蒙昭雪之典。命也如何。虽然。数字 温纶。亦云照烛幽冤。而且使后人公心达识者。操本究末。援彼订此。则足见先人受诬之由。而当时事迹。亦可以举隅而知之也。仆之于贤兄。旧有通家之谊。私自向慕悦服者。实亦不浅焉。而每于稠人广坐之中。望见颜色。挹其清芬。固未尝一日交臂开襟。跪陈心中之事。恒抱不遇之叹。于今始得闻命矣。宁敢讳其狂僭。不尽暴露于左右乎。未知贤兄以为如何也。且其疏中追录言语。有不可卒示外人。重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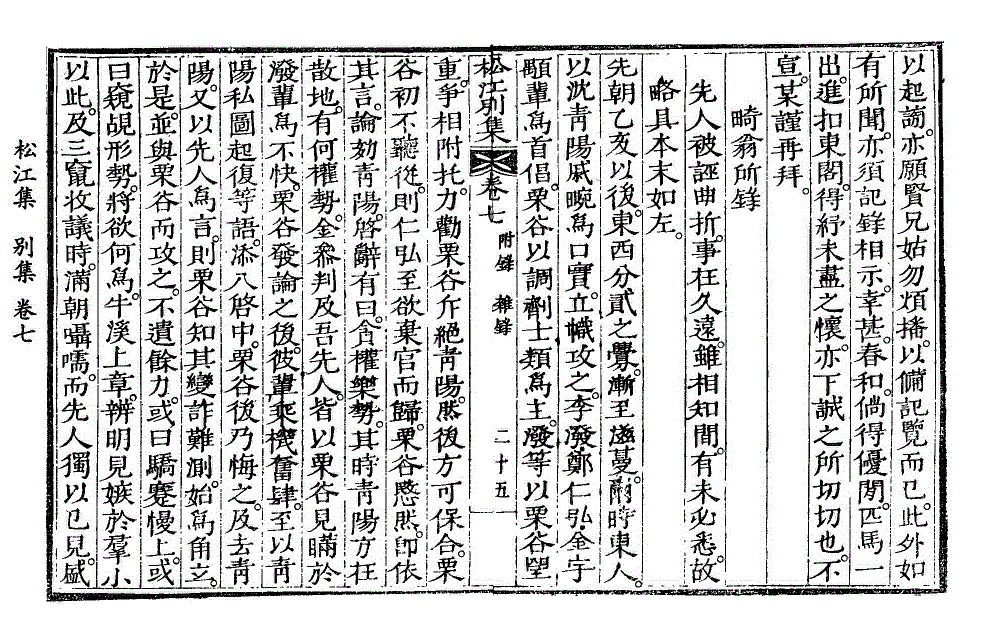 以起谤。亦愿贤兄姑勿烦播。以备记览而已。此外如有所闻。亦须记录相示。幸甚。春和。倘得优閒。匹马一出。进扣东阁。得纾未尽之怀。亦下诚之所切切也。不宣。某谨再拜。
以起谤。亦愿贤兄姑勿烦播。以备记览而已。此外如有所闻。亦须记录相示。幸甚。春和。倘得优閒。匹马一出。进扣东阁。得纾未尽之怀。亦下诚之所切切也。不宣。某谨再拜。畸翁所录
先人被诬曲折。事在久远。虽相知间。有未必悉。故略具本末如左。
先朝乙亥以后。东西分贰之衅。渐至滋蔓。尔时东人。以沈青阳戚畹为口实。立帜攻之。李泼,郑仁弘,金宇颙辈为首倡。栗谷以调剂士类为主。泼等以栗谷望重。争相附托。力劝栗谷斥绝青阳。然后方可保合。栗谷初不听从。则仁弘至欲弃官而归。栗谷悯然即依其言。论劾青阳。启辞有曰。贪权乐势。其时青阳方在散地。有何权势。金参判及吾先人。皆以栗谷见瞒于泼辈为不快。栗谷发论之后。彼辈乘机奋肆。至以青阳私图起复等语。添入启中。栗谷后乃悔之。及去青阳。又以先人为言。则栗谷知其变诈难测。始为角立。于是。并与栗谷而攻之。不遗馀力。或曰骄蹇慢上。或曰窥觇形势。将欲何为。牛溪上章。辨明见嫉于群小以此。及三窜收议时。满朝嗫嚅。而先人独以己见。盛
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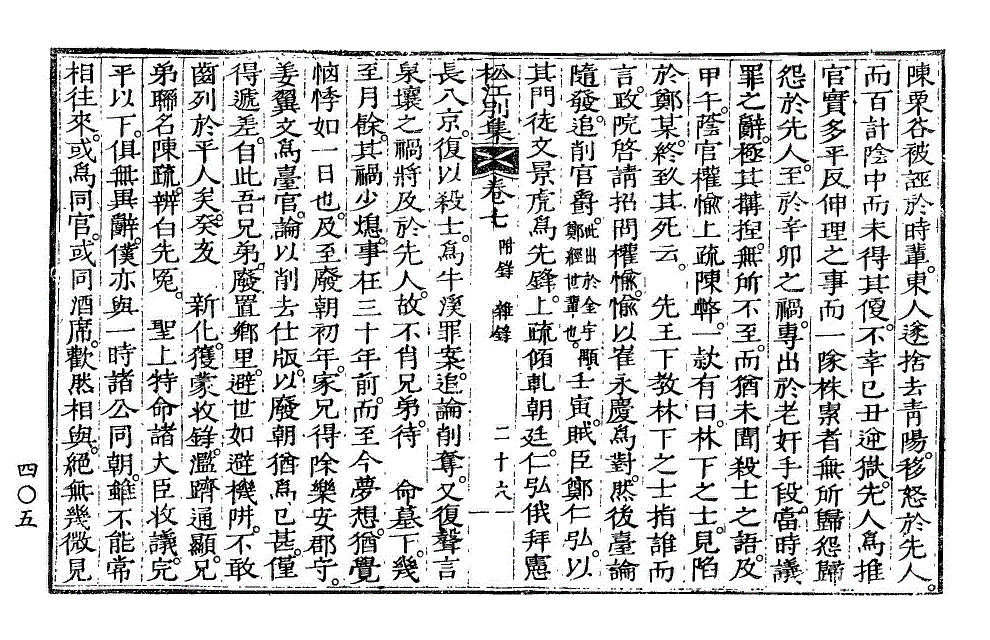 陈栗谷被诬于时辈。东人遂舍去青阳。移怒于先人。而百计阴中而未得其便。不幸己丑逆狱。先人为推官实多平反伸理之事而一队株累者无所归怨归怨于先人。至于辛卯之祸。专出于老奸手段。当时议罪之辞。极其搆捏。无所不至。而犹未闻杀士之语。及甲午。荫官权愉上疏陈弊。一款有曰。林下之士。见陷于郑某。终致其死云。 先王下教林下之士指谁而言。政院启请招问权愉。愉以崔永庆为对。然后台论随发。追削官爵。(此出于金宇颙,郑经世辈也。)壬寅。贼臣郑仁弘。以其门徒文景虎为先锋。上疏倾轧朝廷。仁弘俄拜宪长入京。复以杀士。为牛溪罪案。追论削夺。又复声言泉壤之祸将及于先人。故不肖兄弟。待 命墓下。几至月馀。其祸少熄。事在三十年前。而至今梦想。犹觉恟悸如一日也。及至废朝初年。家兄得除乐安郡守。姜翼文为台官。论以削去仕版。以废朝犹为已甚。仅得递差。自此吾兄弟。废置乡里。避世如避机阱。不敢齿列于平人矣。癸亥 新化。获蒙收录。滥跻通显。兄弟联名陈疏。辨白先冤。 圣上特命诸大臣收议。完平以下。俱无异辞。仆亦与一时诸公同朝。虽不能常相往来。或为同官。或同酒席。欢然相与。绝无几微见
陈栗谷被诬于时辈。东人遂舍去青阳。移怒于先人。而百计阴中而未得其便。不幸己丑逆狱。先人为推官实多平反伸理之事而一队株累者无所归怨归怨于先人。至于辛卯之祸。专出于老奸手段。当时议罪之辞。极其搆捏。无所不至。而犹未闻杀士之语。及甲午。荫官权愉上疏陈弊。一款有曰。林下之士。见陷于郑某。终致其死云。 先王下教林下之士指谁而言。政院启请招问权愉。愉以崔永庆为对。然后台论随发。追削官爵。(此出于金宇颙,郑经世辈也。)壬寅。贼臣郑仁弘。以其门徒文景虎为先锋。上疏倾轧朝廷。仁弘俄拜宪长入京。复以杀士。为牛溪罪案。追论削夺。又复声言泉壤之祸将及于先人。故不肖兄弟。待 命墓下。几至月馀。其祸少熄。事在三十年前。而至今梦想。犹觉恟悸如一日也。及至废朝初年。家兄得除乐安郡守。姜翼文为台官。论以削去仕版。以废朝犹为已甚。仅得递差。自此吾兄弟。废置乡里。避世如避机阱。不敢齿列于平人矣。癸亥 新化。获蒙收录。滥跻通显。兄弟联名陈疏。辨白先冤。 圣上特命诸大臣收议。完平以下。俱无异辞。仆亦与一时诸公同朝。虽不能常相往来。或为同官。或同酒席。欢然相与。绝无几微见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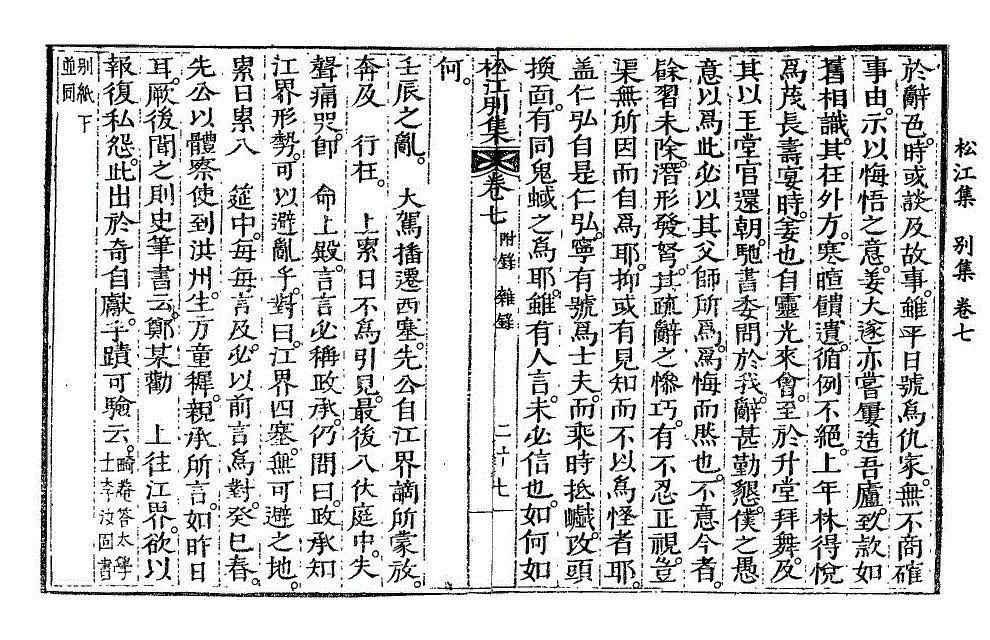 于辞色。时或谈及故事。虽平日号为仇家。无不商确事由。示以悔悟之意。姜大遂亦尝屡造吾庐。致款如旧相识。其在外方。寒暄馈遗。循例不绝。上年林得悦为茂长寿宴时。姜也自灵光来会。至于升堂拜舞。及其以玉堂官还朝。驰书委问于我。辞甚勤恳。仆之愚意以为此必以其父师所为。为悔而然也。不意今者。馀习未除。潜形发弩。其疏辞之惨巧。有不忍正视。岂渠无所因而自为耶。抑或有见知而不以为怪者耶。盖仁弘自是仁弘。宁有号为士夫。而乘时抵巇。改头换面。有同鬼蜮之为耶。虽有人言。未必信也。如何如何。
于辞色。时或谈及故事。虽平日号为仇家。无不商确事由。示以悔悟之意。姜大遂亦尝屡造吾庐。致款如旧相识。其在外方。寒暄馈遗。循例不绝。上年林得悦为茂长寿宴时。姜也自灵光来会。至于升堂拜舞。及其以玉堂官还朝。驰书委问于我。辞甚勤恳。仆之愚意以为此必以其父师所为。为悔而然也。不意今者。馀习未除。潜形发弩。其疏辞之惨巧。有不忍正视。岂渠无所因而自为耶。抑或有见知而不以为怪者耶。盖仁弘自是仁弘。宁有号为士夫。而乘时抵巇。改头换面。有同鬼蜮之为耶。虽有人言。未必信也。如何如何。壬辰之乱。 大驾播迁西塞。先公自江界谪所蒙放。奔及 行在。 上累日不为引见。最后入伏庭中。失声痛哭。即 命上殿。言言必称政承。仍问曰。政承知江界形势。可以避乱乎。对曰。江界四塞。无可避之地。累日累入 筵中。每每言及。必以前言为对。癸巳春。先公以体察使到洪州。生方童稚。亲承所言。如昨日耳。厥后闻之则史笔书云。郑某劝 上往江界。欲以报复私怨。此出于奇自献。手迹可验云。(畸庵答太学士李汝固书别纸下并同)
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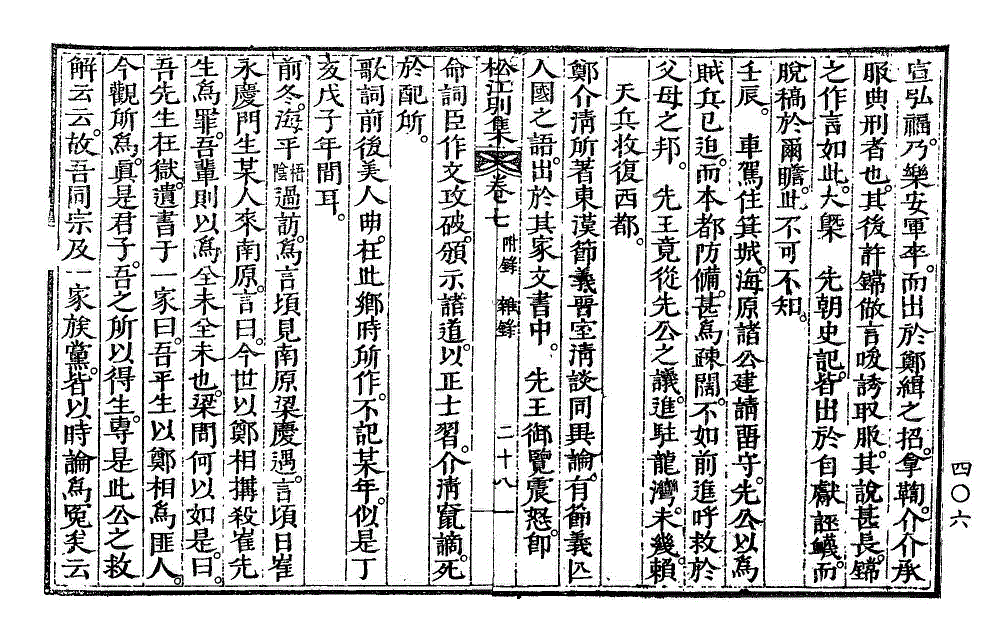 宣弘福。乃乐安军卒。而出于郑缉之招。拿鞫。介介承服典刑者也。其后许鋿做言唆诱取服。其说甚长。鋿之作言如此。大概 先朝史记。皆出于自献诬蔑。而脱稿于尔瞻。此不可不知。
宣弘福。乃乐安军卒。而出于郑缉之招。拿鞫。介介承服典刑者也。其后许鋿做言唆诱取服。其说甚长。鋿之作言如此。大概 先朝史记。皆出于自献诬蔑。而脱稿于尔瞻。此不可不知。壬辰。 车驾住箕城。海原诸公建请留守。先公以为贼兵已迫。而本都防备。甚为疏阔。不如前进呼救于父母之邦。 先王竟从先公之议。进驻龙湾。未几。赖 天兵收复西都。
郑介清所著东汉节义,晋室清谈同异论。有节义亡人国之语。出于其家文书中。 先王御览震怒。即 命词臣作文攻破。颁示诸道。以正士习。介清窜谪。死于配所。
歌词前后美人曲。在此乡时所作。不记某年。似是丁亥戊子年间耳。
前冬。海平(梧阴)过访。为言顷见南原梁庆遇。言顷日崔永庆门生某人来南原。言曰。今世以郑相搆杀崔先生为罪。吾辈则以为全未全未也。梁问何以如是。曰。吾先生在狱。遗书于一家曰。吾平生以郑相为匪人。今观所为。真是君子。吾之所以得生。专是此公之救解云云。故吾同宗及一家族党。皆以时论为冤矣云
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07H 页
 云。(出牛溪集)
云。(出牛溪集)示喻洁家子孙言。尹氏之死。非庚寅五月。乃辛卯五月李阳元委官时云云。尹氏外孙李应男。与仆世居之。知尹氏囚死曲折者。其以此也。己丑十二月。被拿。庚寅正月初旬前囚狱。五月初九日。与其八九诸儿孙。皆被压膝酷刑。诸孙即死。尹氏。初十日死于狱中。庚寅以后十馀年。无杂议。自辛丑后。始以为松相委官时杀之。以其言传相为实。有高传立者。霁峰之孙。从厚之子也。生于安东外家。及长。来居光州。而以西厓为大贤。仰之如山斗。尝以事往安东。则厥处诸生。以传立为少时故旧。人人来访。语及己丑狱。诸生奋臂大言曰。郑澈虽搆杀百崔永庆。不如一尹氏。古今天下。安有如郑澈之毒物乎。传立曰。佥兄之言。何轻发至此。此非松相。乃西厓也。诸生曰。君生长此地。还归故土。反欲趋附郑某之党耶。西厓岂有如是之事。传立曰。是不难知。问于柳袗则可知。俄而袗适来。诸生问之。袗曰。非郑某。乃先人委官时也。满座失色。壬辰变初。松相自谪所入 行朝。与西厓遇于安州。语狱事曰。李泼母。公何不救。西厓曰。势无奈何。尹氏之死。西厓尚不敢讳。他人欲掩之。至于史草。阙而不书
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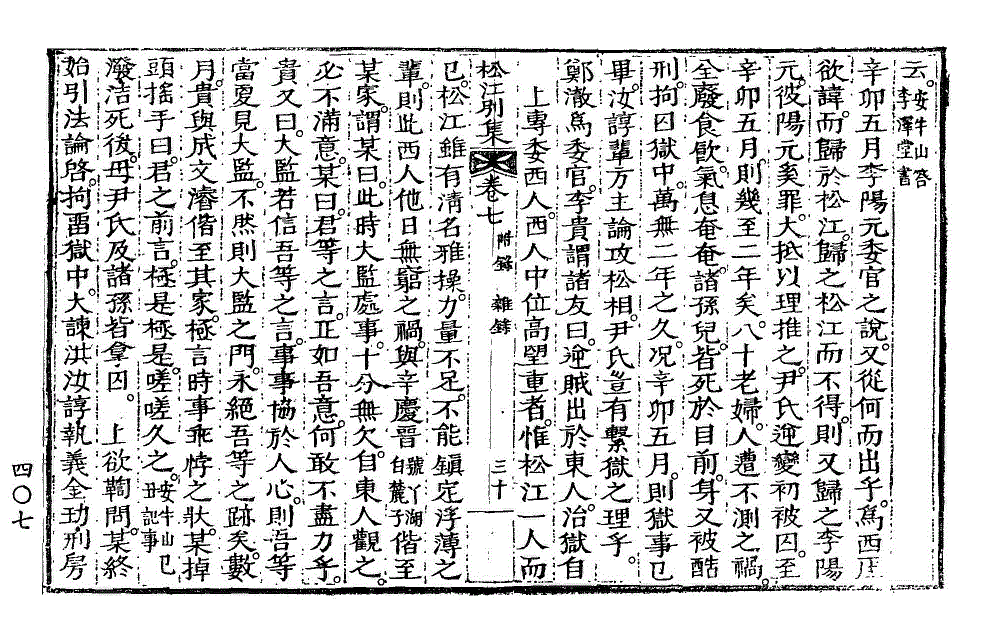 云。(安牛山答李泽堂书)
云。(安牛山答李泽堂书)辛卯五月李阳元委官之说。又从何而出乎。为西厓欲讳。而归于松江。归之松江而不得。则又归之李阳元。彼阳元奚罪。大抵以理推之。尹氏逆变初被囚。至辛卯五月。则几至二年矣。八十老妇。人遭不测之祸。全废食饮。气息奄奄。诸孙儿。皆死于目前。身又被酷刑。拘囚狱中。万无二年之久。况辛卯五月。则狱事已毕。汝谆辈方主论攻松相。尹氏岂有系狱之理乎。 郑澈为委官。李贵谓诸友曰。逆贼出于东人。治狱自 上专委西人。西人中位高望重者。惟松江一人而已。松江虽有清名雅操。力量不足。不能镇定浮薄之辈。则此西人他日无穷之祸。与辛庆晋(号丫湖白麓子)偕至某家。谓某曰。此时大监处事。十分无欠。自东人观之。必不满意。某曰。君等之言。正如吾意。何敢不尽力乎。贵又曰。大监若信吾等之言。事事协于人心。则吾等当更见大监。不然则大监之门。永绝吾等之迹矣。数月。贵与成文浚偕至其家。极言时事乖悖之状。某掉头摇手曰。君之前言。极是极是。嗟嗟久之。( 安牛山己丑记事)泼,洁死后。母尹氏及诸孙皆拿囚。 上欲鞫问。某终始引法论启。拘留狱中。大谏洪汝谆,执义金玏,刑房
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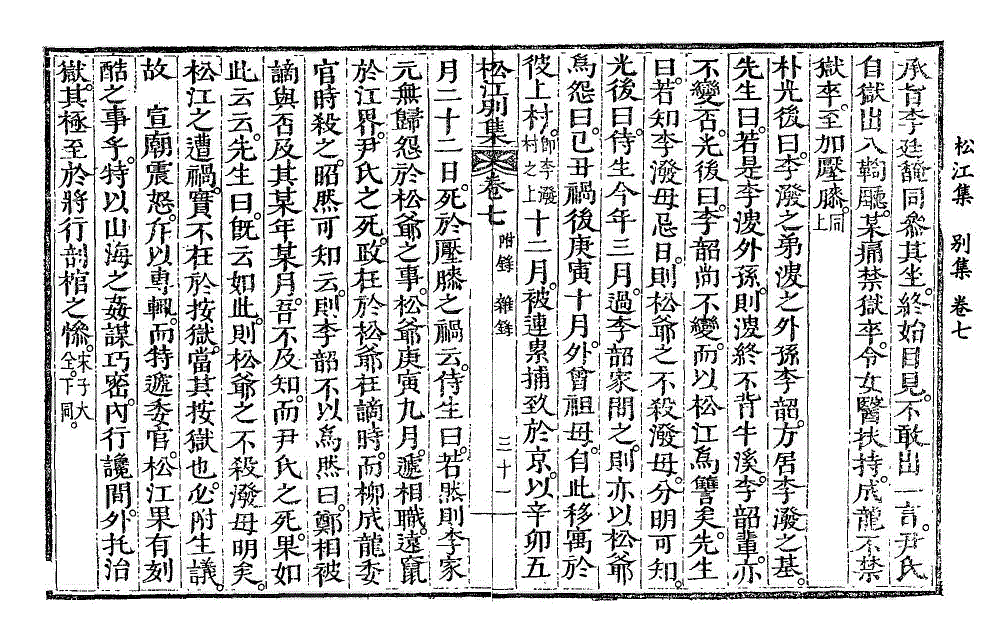 承旨李廷馣同参其坐。终始目见。不敢出一言。尹氏自狱出入鞫厅。某痛禁狱卒。令女医扶持。成龙不禁狱卒。至加压膝。(同上)
承旨李廷馣同参其坐。终始目见。不敢出一言。尹氏自狱出入鞫厅。某痛禁狱卒。令女医扶持。成龙不禁狱卒。至加压膝。(同上)朴光后曰。李泼之弟溭之外孙李韶。方居李泼之基。先生曰。若是李溭外孙。则溭终不背牛溪。李韶辈。亦不变否。光后曰。李韶尚不变。而以松江为雠矣。先生曰。若知李泼母忌日。则松爷之不杀泼母。分明可知。光后曰。侍生今年三月。过李韶家问之。则亦以松爷为怨曰。己丑祸后庚寅十月。外曾祖母。自此移寓于彼上村。(即李泼村之上)十二月。被连累捕致于京。以辛卯五月二十二日。死于压膝之祸云。待生曰。若然则李家元无归怨于松爷之事。松爷庚寅九月。递相职。远窜于江界。尹氏之死。政在于松爷在谪时。而柳成龙委官时杀之。昭然可知云。则李韶不以为然曰。郑相被谪与否及其某年某月。吾不及知。而尹氏之死。果如此云云。先生曰。既云如此。则松爷之不杀泼母明矣。松江之遭祸。实不在于按狱。当其按狱也。必附生议。故 宣庙震怒。斥以专辄。而特递委官。松江果有刻酷之事乎。特以山海之奸谋巧密。内行谗间。外托治狱。其极至于将行剖棺之惨。(宋子大全。下同。)
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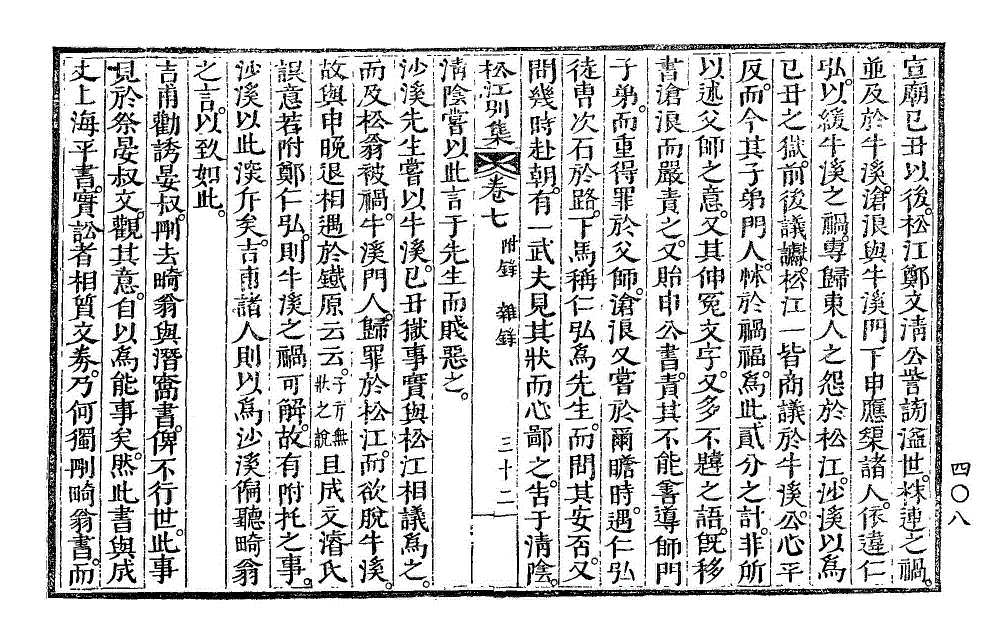 宣庙己丑以后。松江郑文清公訾谤溢世。株连之祸。并及于牛溪。沧浪与牛溪门下申应矩诸人。依违仁弘。以缓牛溪之祸。专归东人之怨于松江。沙溪以为己丑之狱。前后议谳。松江一皆商议于牛溪。公心平反。而今其子弟门人。怵于祸福。为此贰分之计。非所以述父师之意。又其伸冤文字。又多不韪之语。既移书沧浪而严责之。又贻申公书。责其不能善导师门子弟。而重得罪于父师。沧浪又尝于尔瞻时。遇仁弘徒曹次石于路。下马称仁弘为先生。而问其安否。又问几时赴朝。有一武夫见其状而心鄙之。告于清阴。清阴尝以此言于先生而贱恶之。
宣庙己丑以后。松江郑文清公訾谤溢世。株连之祸。并及于牛溪。沧浪与牛溪门下申应矩诸人。依违仁弘。以缓牛溪之祸。专归东人之怨于松江。沙溪以为己丑之狱。前后议谳。松江一皆商议于牛溪。公心平反。而今其子弟门人。怵于祸福。为此贰分之计。非所以述父师之意。又其伸冤文字。又多不韪之语。既移书沧浪而严责之。又贻申公书。责其不能善导师门子弟。而重得罪于父师。沧浪又尝于尔瞻时。遇仁弘徒曹次石于路。下马称仁弘为先生。而问其安否。又问几时赴朝。有一武夫见其状而心鄙之。告于清阴。清阴尝以此言于先生而贱恶之。沙溪先生尝以牛溪。己丑狱事实与松江相议为之。而及松翁被祸。牛溪门人。归罪于松江。而欲脱牛溪。故与申晚退相遇于铁原云云。(子方无状之说)且成文浚氏误意若附郑仁弘。则牛溪之祸可解。故有附托之事。沙溪以此深斥矣。吉甫诸人则以为沙溪偏听畸翁之言。以致如此。
吉甫劝诱晏叔。删去畸翁与潜窝书。俾不行世。此事见于祭晏叔文。观其意。自以为能事矣。然此书与成丈上海平书。实讼者相质文券。乃何独删畸翁书。而
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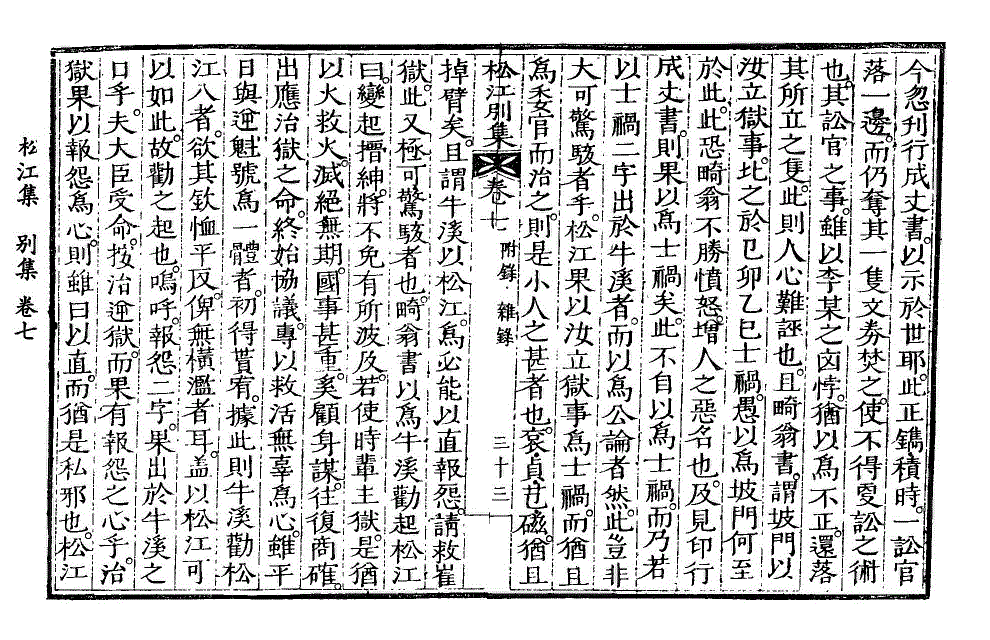 今忽刊行成丈书。以示于世耶。此正镌,积时。一讼官落一边。而仍夺其一只文券焚之。使不得更讼之术也。其讼官之事。虽以李某之凶悖。犹以为不正。还落其所立之只。此则人心难诬也。且畸翁书。谓坡门以汝立狱事。比之于己卯乙巳士祸。愚以为坡门何至于此。此恐畸翁不胜愤怒。增人之恶名也。及见印行成丈书。则果以为士祸矣。此不自以为士祸。而乃若以士祸二字出于牛溪者。而以为公论者然。此岂非大可惊骇者乎。松江果以汝立狱事为士祸。而犹且为委官而治之。则是小人之甚者也。衮,贞,芑,磁。犹且掉臂矣。且谓牛溪以松江。为必能以直报怨。请救崔狱。此又极可惊骇者也。畸翁书以为牛溪劝起松江曰。变起搢绅。将不免有所波及。若使时辈主狱。是犹以火救火。灭绝无期。国事甚重。奚顾身谋。往复商确。出应治狱之命。终始协议。专以救活无辜为心。虽平日与逆魁号为一体者。初得贳宥。据此则牛溪劝松江入者。欲其钦恤平反。俾无横滥者耳。盖以松江可以如此。故劝之起也。呜呼。报怨二字。果出于牛溪之口乎。夫大臣受命。按治逆狱。而果有报怨之心乎。治狱果以报怨为心。则虽曰以直。而犹是私邪也。松江
今忽刊行成丈书。以示于世耶。此正镌,积时。一讼官落一边。而仍夺其一只文券焚之。使不得更讼之术也。其讼官之事。虽以李某之凶悖。犹以为不正。还落其所立之只。此则人心难诬也。且畸翁书。谓坡门以汝立狱事。比之于己卯乙巳士祸。愚以为坡门何至于此。此恐畸翁不胜愤怒。增人之恶名也。及见印行成丈书。则果以为士祸矣。此不自以为士祸。而乃若以士祸二字出于牛溪者。而以为公论者然。此岂非大可惊骇者乎。松江果以汝立狱事为士祸。而犹且为委官而治之。则是小人之甚者也。衮,贞,芑,磁。犹且掉臂矣。且谓牛溪以松江。为必能以直报怨。请救崔狱。此又极可惊骇者也。畸翁书以为牛溪劝起松江曰。变起搢绅。将不免有所波及。若使时辈主狱。是犹以火救火。灭绝无期。国事甚重。奚顾身谋。往复商确。出应治狱之命。终始协议。专以救活无辜为心。虽平日与逆魁号为一体者。初得贳宥。据此则牛溪劝松江入者。欲其钦恤平反。俾无横滥者耳。盖以松江可以如此。故劝之起也。呜呼。报怨二字。果出于牛溪之口乎。夫大臣受命。按治逆狱。而果有报怨之心乎。治狱果以报怨为心。则虽曰以直。而犹是私邪也。松江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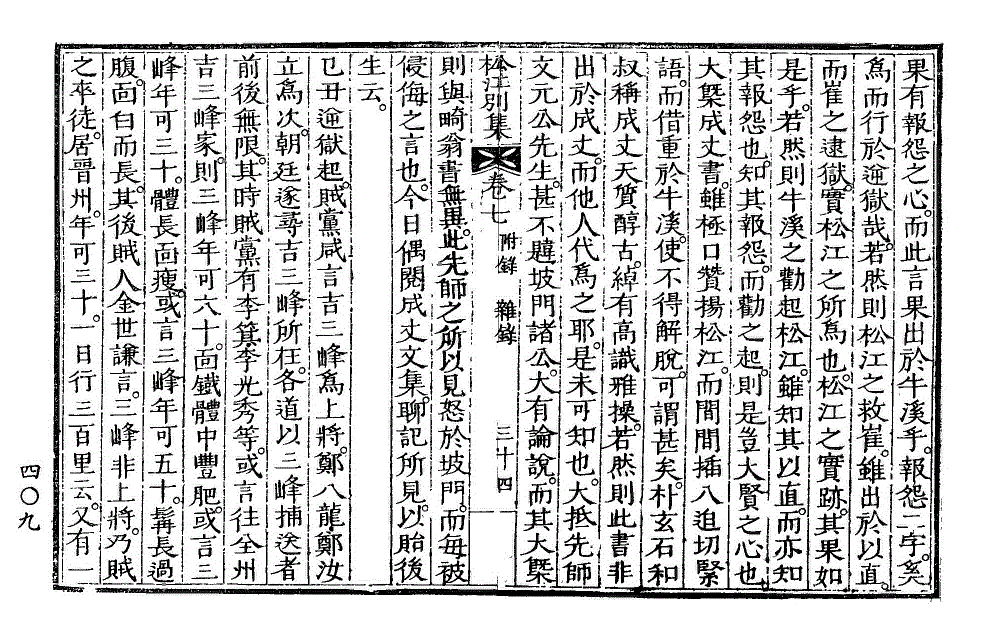 果有报怨之心。而此言果出于牛溪乎。报怨二字。奚为而行于逆狱哉。若然则松江之救崔。虽出于以直。而崔之逮狱。实松江之所为也。松江之实迹。其果如是乎。若然则牛溪之劝起松江。虽知其以直。而亦知其报怨也。知其报怨。而劝之起。则是岂大贤之心也。大概成丈书。虽极口赞扬松江。而间间插入迫切紧语。而借重于牛溪。使不得解脱。可谓甚矣。朴玄石和叔称成丈天质醇古。绰有高识雅操。若然则此书非出于成丈。而他人代为之耶。是未可知也。大抵先师文元公先生。甚不韪坡门诸公。大有论说。而其大概则与畸翁书无异。此先师之所以见怒于坡门。而每被侵侮之言也。今日偶阅成丈文集。聊记所见。以贻后生云。
果有报怨之心。而此言果出于牛溪乎。报怨二字。奚为而行于逆狱哉。若然则松江之救崔。虽出于以直。而崔之逮狱。实松江之所为也。松江之实迹。其果如是乎。若然则牛溪之劝起松江。虽知其以直。而亦知其报怨也。知其报怨。而劝之起。则是岂大贤之心也。大概成丈书。虽极口赞扬松江。而间间插入迫切紧语。而借重于牛溪。使不得解脱。可谓甚矣。朴玄石和叔称成丈天质醇古。绰有高识雅操。若然则此书非出于成丈。而他人代为之耶。是未可知也。大抵先师文元公先生。甚不韪坡门诸公。大有论说。而其大概则与畸翁书无异。此先师之所以见怒于坡门。而每被侵侮之言也。今日偶阅成丈文集。聊记所见。以贻后生云。己丑逆狱起。贼党咸言吉三峰为上将。郑八龙,郑汝立为次。朝廷遂寻吉三峰所在。各道以三峰捕送者前后无限。其时贼党有李箕,李光秀等。或言往全州吉三峰家。则三峰年可六十。面铁体中丰肥。或言三峰年可三十。体长面瘦。或言三峰年可五十。髯长过腹。面白而长。其后贼人金世谦言。三峰非上将。乃贼之卒徒。居晋州。年可三十。一日行三百里云。又有一
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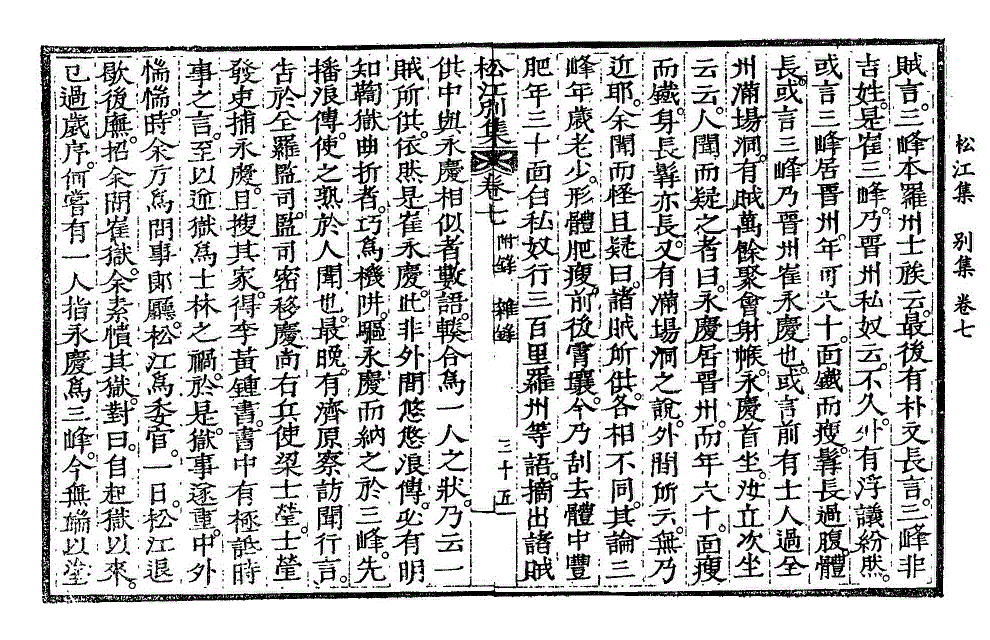 贼言。三峰本罗州士族云。最后有朴文长言。三峰非吉姓。是崔三峰。乃晋州私奴云。不久。外有浮议纷然。或言三峰居晋州。年可六十。面铁而瘦。髯长过腹。体长。或言三峰乃晋州崔永庆也。或言前有士人过全州满场洞。有贼万馀聚会射帿。永庆首坐。汝立次坐云云。人闻而疑之者曰。永庆居晋州。而年六十。面瘦而铁。身长髯亦长。又有满场洞之说。外间所云。无乃近耶。余闻而怪且疑曰。诸贼所供。各相不同。其论三峰年岁老少。形体肥瘦。前后霄壤。今乃刮去体中丰肥年三十面白私奴行三百里罗州等语。摘出诸贼供中与永庆相似者数语。辏合为一人之状。乃云一贼所供。依然是崔永庆。此非外间悠悠浪传。必有明知鞫狱曲折者。巧为机阱。驱永庆而纳之于三峰。先播浪传。使之熟于人闻也。最晚。有济原察访闻行言。告于全罗监司。监司密移庆尚右兵使梁士莹。士莹发吏捕永庆。且搜其家。得李黄钟书。书中有极诋时事之言。至以逆狱为士林之祸。于是。狱事遂重。中外惴惴。时余方为问事郎厅。松江为委官。一日。松江退歇后庑。招余闻崔狱。余素愤其狱。对曰。自起狱以来。已过岁序。何尝有一人指永庆为三峰。今无端以涂
贼言。三峰本罗州士族云。最后有朴文长言。三峰非吉姓。是崔三峰。乃晋州私奴云。不久。外有浮议纷然。或言三峰居晋州。年可六十。面铁而瘦。髯长过腹。体长。或言三峰乃晋州崔永庆也。或言前有士人过全州满场洞。有贼万馀聚会射帿。永庆首坐。汝立次坐云云。人闻而疑之者曰。永庆居晋州。而年六十。面瘦而铁。身长髯亦长。又有满场洞之说。外间所云。无乃近耶。余闻而怪且疑曰。诸贼所供。各相不同。其论三峰年岁老少。形体肥瘦。前后霄壤。今乃刮去体中丰肥年三十面白私奴行三百里罗州等语。摘出诸贼供中与永庆相似者数语。辏合为一人之状。乃云一贼所供。依然是崔永庆。此非外间悠悠浪传。必有明知鞫狱曲折者。巧为机阱。驱永庆而纳之于三峰。先播浪传。使之熟于人闻也。最晚。有济原察访闻行言。告于全罗监司。监司密移庆尚右兵使梁士莹。士莹发吏捕永庆。且搜其家。得李黄钟书。书中有极诋时事之言。至以逆狱为士林之祸。于是。狱事遂重。中外惴惴。时余方为问事郎厅。松江为委官。一日。松江退歇后庑。招余闻崔狱。余素愤其狱。对曰。自起狱以来。已过岁序。何尝有一人指永庆为三峰。今无端以涂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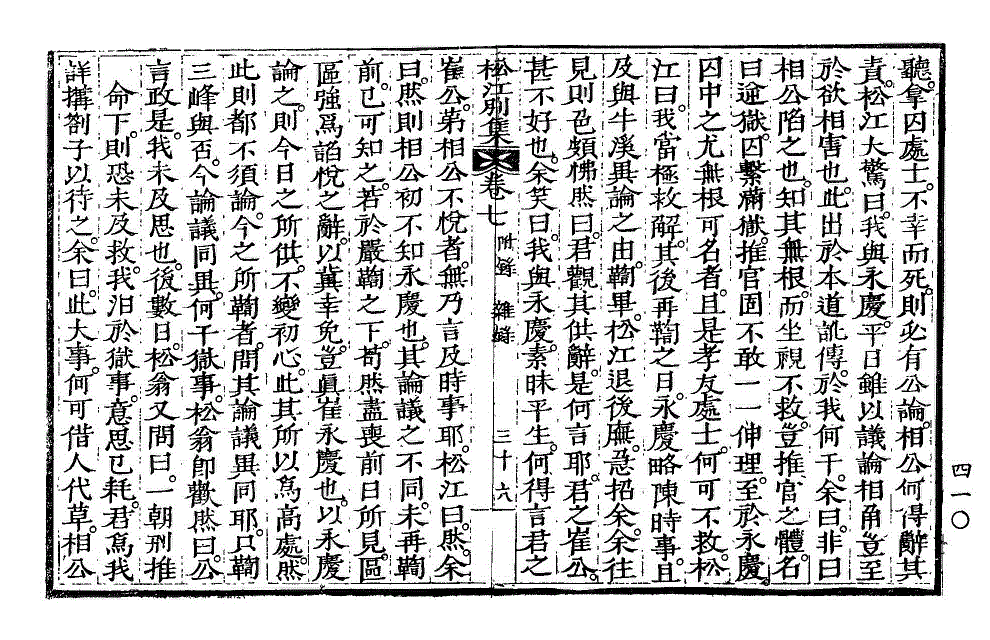 听。拿囚处士。不幸而死。则必有公论。相公何得辞其责。松江大惊曰。我与永庆。平日虽以议论相角岂至于欲相害也。此出于本道讹传。于我何干。余曰。非曰相公陷之也。知其无根。而坐视不救。岂推官之体。名曰逆狱。囚系满狱。推官固不敢一一伸理。至于永庆。囚中之尤无根可名者。且是孝友处士。何可不救。松江曰。我当极救解。其后再鞫之日。永庆略陈时事。且及与牛溪异论之由。鞫毕。松江退后庑。急招余。余往见则色颇怫然曰。君观其供辞。是何言耶。君之崔公。甚不好也。余笑曰。我与永庆。素昧平生。何得言君之崔公。第相公不悦者。无乃言及时事耶。松江曰。然。余曰。然则相公初不知永庆也。其论议之不同。未再鞫前。已可知之。若于严鞫之下。苟然尽丧前日所见。区区强为谄悦之辞。以冀幸免。岂真崔永庆也。以永庆论之。则今日之所供。不变初心。此其所以为高处。然此则都不须论。今之所鞫者。问其论议异同耶。只鞫三峰与否。今论议同异。何干狱事。松翁即欢然曰。公言政是。我未及思也。后数日。松翁又问曰。一朝刑推 命下。则恐未及救。我汨于狱事。意思已耗。君为我详搆劄子以待之。余曰。此大事。何可借人代草。相公
听。拿囚处士。不幸而死。则必有公论。相公何得辞其责。松江大惊曰。我与永庆。平日虽以议论相角岂至于欲相害也。此出于本道讹传。于我何干。余曰。非曰相公陷之也。知其无根。而坐视不救。岂推官之体。名曰逆狱。囚系满狱。推官固不敢一一伸理。至于永庆。囚中之尤无根可名者。且是孝友处士。何可不救。松江曰。我当极救解。其后再鞫之日。永庆略陈时事。且及与牛溪异论之由。鞫毕。松江退后庑。急招余。余往见则色颇怫然曰。君观其供辞。是何言耶。君之崔公。甚不好也。余笑曰。我与永庆。素昧平生。何得言君之崔公。第相公不悦者。无乃言及时事耶。松江曰。然。余曰。然则相公初不知永庆也。其论议之不同。未再鞫前。已可知之。若于严鞫之下。苟然尽丧前日所见。区区强为谄悦之辞。以冀幸免。岂真崔永庆也。以永庆论之。则今日之所供。不变初心。此其所以为高处。然此则都不须论。今之所鞫者。问其论议异同耶。只鞫三峰与否。今论议同异。何干狱事。松翁即欢然曰。公言政是。我未及思也。后数日。松翁又问曰。一朝刑推 命下。则恐未及救。我汨于狱事。意思已耗。君为我详搆劄子以待之。余曰。此大事。何可借人代草。相公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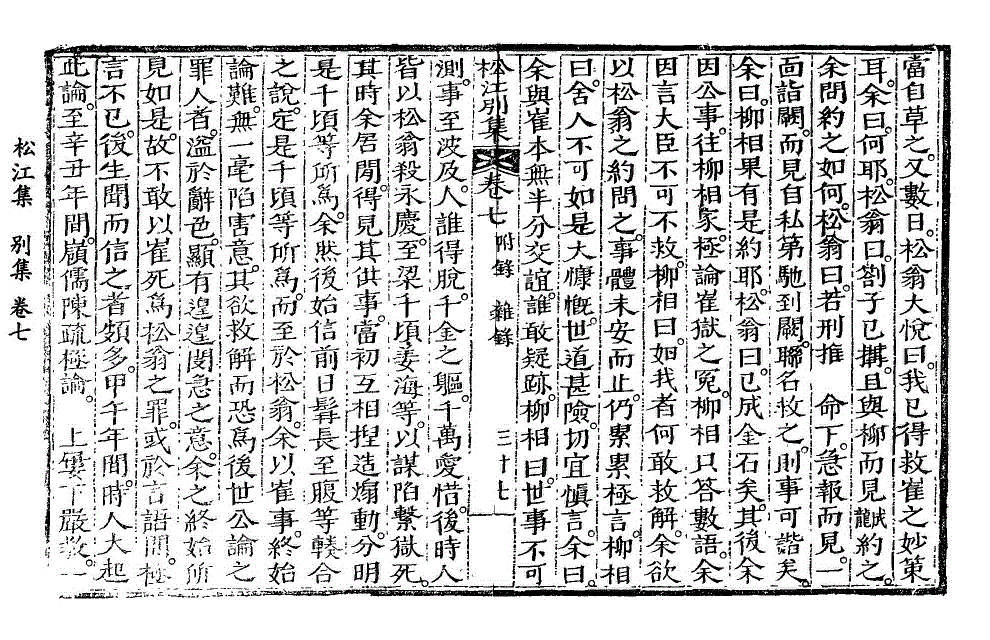 当自草之。又数日。松翁大悦曰。我已得救崔之妙策耳。余曰。何耶。松翁曰。劄子已搆。且与柳而见(成龙)约之。余问约之如何。松翁曰。若刑推 命下。急报而见。一面诣阙。而见自私第驰到阙。联名救之。则事可谐矣。余曰。柳相果有是约耶。松翁曰。已成金石矣。其后余因公事。往柳相家。极论崔狱之冤。柳相只答数语。余因言大臣不可不救。柳相曰。如我者何敢救解。余欲以松翁之约问之。事体未安而止。仍累累极言。柳相曰。舍人不可如是大慷慨。世道甚险。切宜慎言。余曰。余与崔本无半分交谊。谁敢疑迹。柳相曰。世事不可测。事至波及。人谁得脱。千金之躯。千万爱惜。后时人皆以松翁杀永庆。至梁千顷姜海等。以谋陷系狱死。其时余居閒。得见其供事。当初互相捏造煽动。分明是千顷等所为。余然后始信前日髯长至腹等辏合之说。定是千顷等所为。而至于松翁。余以崔事。终始论难。无一毫陷害意。其欲救解而恐为后世公论之罪人者。溢于辞色。显有遑遑闵急之意。余之终始所见如是。故不敢以崔死为松翁之罪。或于言语间。极言不已。后生闻而信之者颇多。甲午年间。时人大起此论。至辛丑年间。岭儒陈疏极论。 上屡下严教。一
当自草之。又数日。松翁大悦曰。我已得救崔之妙策耳。余曰。何耶。松翁曰。劄子已搆。且与柳而见(成龙)约之。余问约之如何。松翁曰。若刑推 命下。急报而见。一面诣阙。而见自私第驰到阙。联名救之。则事可谐矣。余曰。柳相果有是约耶。松翁曰。已成金石矣。其后余因公事。往柳相家。极论崔狱之冤。柳相只答数语。余因言大臣不可不救。柳相曰。如我者何敢救解。余欲以松翁之约问之。事体未安而止。仍累累极言。柳相曰。舍人不可如是大慷慨。世道甚险。切宜慎言。余曰。余与崔本无半分交谊。谁敢疑迹。柳相曰。世事不可测。事至波及。人谁得脱。千金之躯。千万爱惜。后时人皆以松翁杀永庆。至梁千顷姜海等。以谋陷系狱死。其时余居閒。得见其供事。当初互相捏造煽动。分明是千顷等所为。余然后始信前日髯长至腹等辏合之说。定是千顷等所为。而至于松翁。余以崔事。终始论难。无一毫陷害意。其欲救解而恐为后世公论之罪人者。溢于辞色。显有遑遑闵急之意。余之终始所见如是。故不敢以崔死为松翁之罪。或于言语间。极言不已。后生闻而信之者颇多。甲午年间。时人大起此论。至辛丑年间。岭儒陈疏极论。 上屡下严教。一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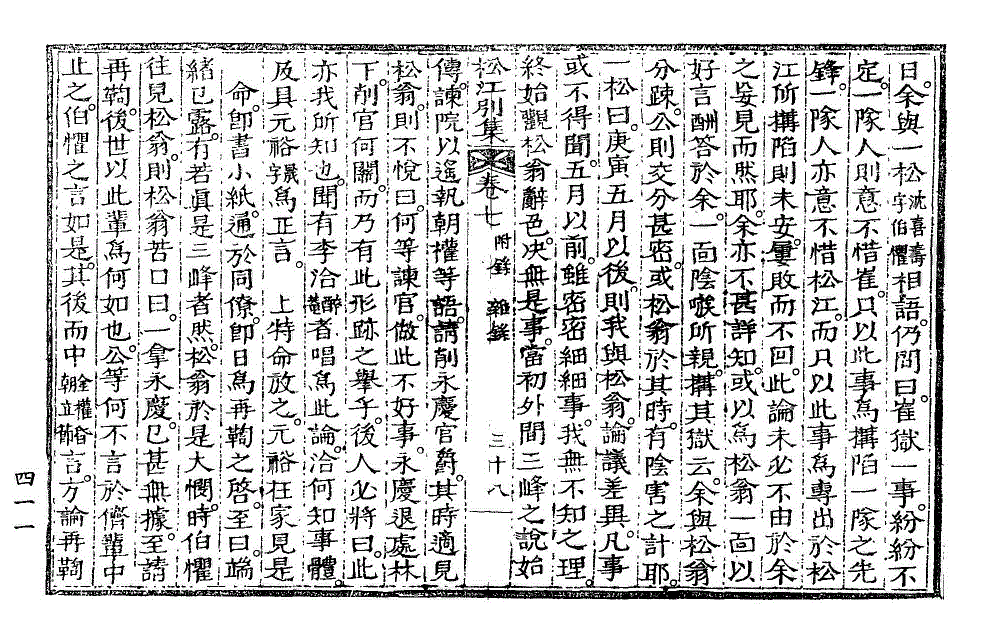 日。余与一松(沈喜寿字伯惧)相语。仍问曰。崔狱一事。纷纷不定。一队人则意不惜崔。只以此事为搆陷一队之先锋。一队人亦意不惜松江。而只以此事为专出于松江所搆陷则未安。屡败而不回。此论未必不由于余之妄见而然耶。余亦不甚详知。或以为松翁一面以好言酬答于余。一面阴嗾所亲。搆其狱云。余与松翁分疏。公则交分甚密。或松翁于其时。有阴害之计耶。一松曰。庚寅五月以后。则我与松翁。论议差异。凡事或不得闻。五月以前。虽密密细细事。我无不知之理。终始观松翁辞色。决无是事。当初外间三峰之说始传。谏院以遥执朝权等语。请削永庆官爵。其时适见松翁。则不悦曰。何等谏官。做此不好事。永庆退处林下。削官何关。而乃有此形迹之举乎。后人必将曰。此亦我所知也。闻有李洽(醉庵)者唱为此论。洽何知事体。及具元裕(晟字)为正言。 上特命放之。元裕在家见是 命。即书小纸。通于同僚。即日为再鞫之启。至曰。端绪已露。有若真是三峰者然。松翁于是大悯。时伯惧往见松翁。则松翁若口曰。一拿永庆。已甚无据。至请再鞫。后世以此辈为何如也。公等何不言于侪辈中止之。伯惧之言如是。其后而中(金权昏朝立节)言。方论再鞫
日。余与一松(沈喜寿字伯惧)相语。仍问曰。崔狱一事。纷纷不定。一队人则意不惜崔。只以此事为搆陷一队之先锋。一队人亦意不惜松江。而只以此事为专出于松江所搆陷则未安。屡败而不回。此论未必不由于余之妄见而然耶。余亦不甚详知。或以为松翁一面以好言酬答于余。一面阴嗾所亲。搆其狱云。余与松翁分疏。公则交分甚密。或松翁于其时。有阴害之计耶。一松曰。庚寅五月以后。则我与松翁。论议差异。凡事或不得闻。五月以前。虽密密细细事。我无不知之理。终始观松翁辞色。决无是事。当初外间三峰之说始传。谏院以遥执朝权等语。请削永庆官爵。其时适见松翁。则不悦曰。何等谏官。做此不好事。永庆退处林下。削官何关。而乃有此形迹之举乎。后人必将曰。此亦我所知也。闻有李洽(醉庵)者唱为此论。洽何知事体。及具元裕(晟字)为正言。 上特命放之。元裕在家见是 命。即书小纸。通于同僚。即日为再鞫之启。至曰。端绪已露。有若真是三峰者然。松翁于是大悯。时伯惧往见松翁。则松翁若口曰。一拿永庆。已甚无据。至请再鞫。后世以此辈为何如也。公等何不言于侪辈中止之。伯惧之言如是。其后而中(金权昏朝立节)言。方论再鞫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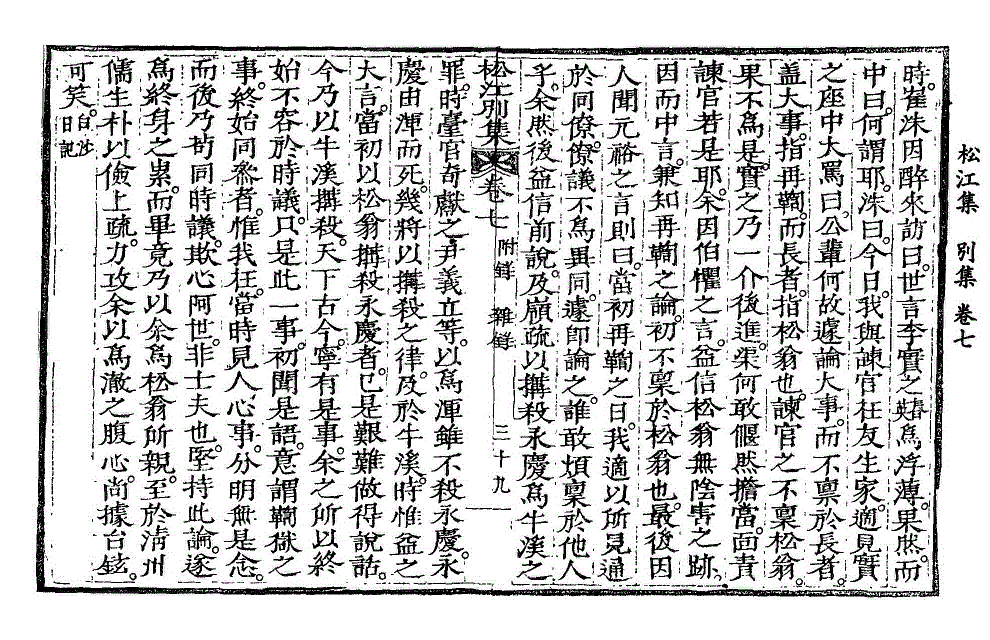 时。崔洙因醉来访曰。世言李实之(春英)为浮薄。果然。而中曰。何谓耶。洙曰。今日。我与谏官在友生家。适见实之座中大骂曰。公辈何故遽论大事。而不禀于长者。盖大事。指再鞫。而长者。指松翁也。谏官之不禀松翁。果不为是。实之乃一介后进。渠何敢偃然担当。面责谏官若是耶。余因伯惧之言。益信松翁无阴害之迹。因而中言。兼知再鞫之论。初不禀于松翁也。最后因人闻元裕之言则曰。当初再鞫之日。我适以所见通于同僚。僚议不为异同。遽即论之。谁敢烦禀于他人乎。余然后益信前说。及岭疏以搆杀永庆为牛溪之罪。时台官奇献之,尹义立等。以为浑虽不杀永庆。永庆由浑而死。几将以搆杀之律。及于牛溪。时惟益之大言。当初以松翁搆杀永庆者。已是艰难做得说话。今乃以牛溪搆杀。天下古今。宁有是事。余之所以终始不容于时议。只是此一事。初闻是语。意谓鞫狱之事。终始同参者。惟我在。当时见人心事。分明无是念。而后乃苟同时议。欺心阿世。非士夫也。坚持此论。遂为终身之累。而毕竟乃以余为松翁所亲。至于清州儒生朴以俭上疏。力攻余以为澈之腹心。尚据台铉。可笑。(白沙日记)
时。崔洙因醉来访曰。世言李实之(春英)为浮薄。果然。而中曰。何谓耶。洙曰。今日。我与谏官在友生家。适见实之座中大骂曰。公辈何故遽论大事。而不禀于长者。盖大事。指再鞫。而长者。指松翁也。谏官之不禀松翁。果不为是。实之乃一介后进。渠何敢偃然担当。面责谏官若是耶。余因伯惧之言。益信松翁无阴害之迹。因而中言。兼知再鞫之论。初不禀于松翁也。最后因人闻元裕之言则曰。当初再鞫之日。我适以所见通于同僚。僚议不为异同。遽即论之。谁敢烦禀于他人乎。余然后益信前说。及岭疏以搆杀永庆为牛溪之罪。时台官奇献之,尹义立等。以为浑虽不杀永庆。永庆由浑而死。几将以搆杀之律。及于牛溪。时惟益之大言。当初以松翁搆杀永庆者。已是艰难做得说话。今乃以牛溪搆杀。天下古今。宁有是事。余之所以终始不容于时议。只是此一事。初闻是语。意谓鞫狱之事。终始同参者。惟我在。当时见人心事。分明无是念。而后乃苟同时议。欺心阿世。非士夫也。坚持此论。遂为终身之累。而毕竟乃以余为松翁所亲。至于清州儒生朴以俭上疏。力攻余以为澈之腹心。尚据台铉。可笑。(白沙日记)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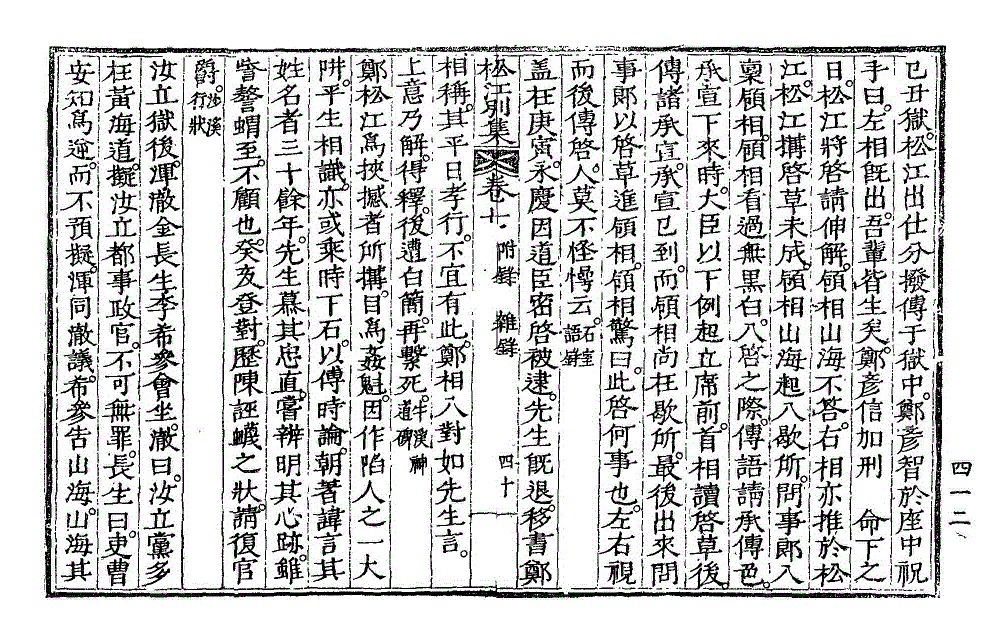 己丑狱。松江出仕分拨传于狱中。郑彦智于座中祝手曰。左相既出。吾辈皆生矣。郑彦信加刑 命下之日。松江将启请伸解。领相山海不答。古相亦推于松江。松江搆启草未成。领相山海起入歇所。问事郎入禀领相。领相看过无黑白。入启之际。传语请承传色。承宣下来时。大臣以下例起立席前。首相读启草后。传诸承宣。承宣已到。而领相尚在歇所。最后出来问事郎以启草进领相。领相惊曰。此启何事也。左右视而后传启。人莫不怪愕云。(石室语录)
己丑狱。松江出仕分拨传于狱中。郑彦智于座中祝手曰。左相既出。吾辈皆生矣。郑彦信加刑 命下之日。松江将启请伸解。领相山海不答。古相亦推于松江。松江搆启草未成。领相山海起入歇所。问事郎入禀领相。领相看过无黑白。入启之际。传语请承传色。承宣下来时。大臣以下例起立席前。首相读启草后。传诸承宣。承宣已到。而领相尚在歇所。最后出来问事郎以启草进领相。领相惊曰。此启何事也。左右视而后传启。人莫不怪愕云。(石室语录)盖在庚寅。永庆因道臣密启被逮。先生既退。移书郑相称。其平日孝行。不宜有此。郑相入对如先生言。 上意乃解。得释。后遭白简。再系死。(牛溪神道碑)郑松江为挟撼者所搆。目为奸魁。因作陷人之一大阱。平生相识。亦或乘时下石。以传时论。朝著讳言其姓名者三十馀年。先生慕其忠直。尝辨明其心迹。虽訾謷猬至。不顾也。癸亥登对。历陈诬蔑之状。请复官爵。(沙溪行状)
汝立狱后。浑,澈金长生,李希参会坐。澈曰。汝立党多在黄海道。拟汝立都事政官。不可无罪。长生曰。吏曹安知为逆。而不预拟。浑同澈议。希参告山海。山海其
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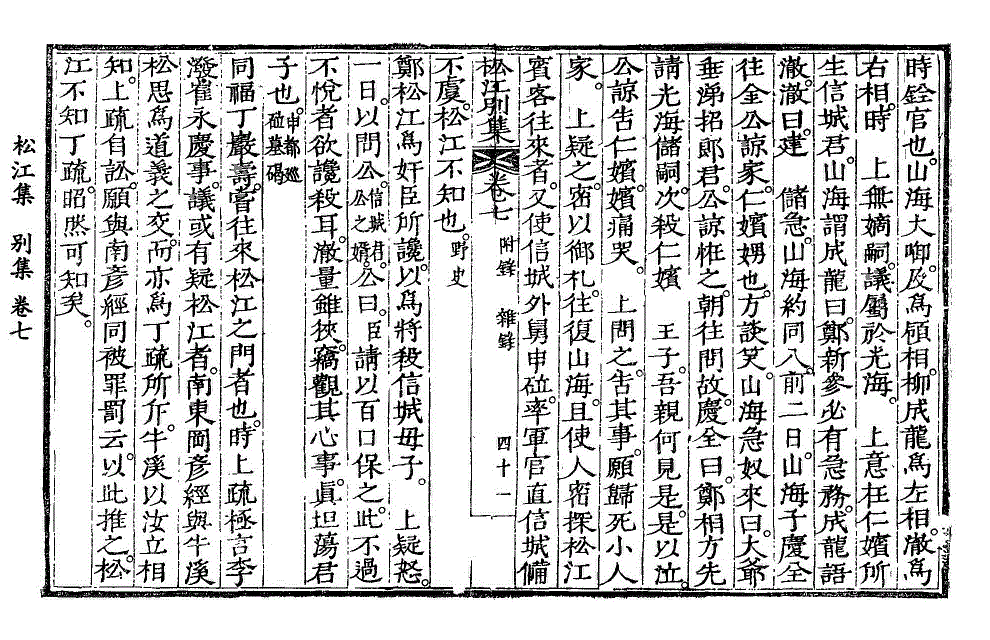 时铨官也。山海大衔。及为领相。柳成龙为左相。澈为右相。时 上无嫡嗣。议属于光海。 上意在仁嫔所生信城君。山海谓成龙曰。郑新参必有急务。成龙语澈。澈曰。建 储急。山海约同入。前二日。山海子庆全往金公谅家。仁嫔喃也。方谈笑。山海急奴来曰。大爷垂涕招郎君。公谅怪之。朝往问故。庆全曰。郑相方先请光海储嗣。次杀仁嫔 王子。吾亲何见是。是以泣。公谅告仁嫔。嫔痛哭。 上问之。告其事。愿归死小人家。 上疑之。密以御札。往复山海。且使人密探松江宾客往来者。又使信城外舅申砬。率军官直信城备不虞。松江不知也。(野史)
时铨官也。山海大衔。及为领相。柳成龙为左相。澈为右相。时 上无嫡嗣。议属于光海。 上意在仁嫔所生信城君。山海谓成龙曰。郑新参必有急务。成龙语澈。澈曰。建 储急。山海约同入。前二日。山海子庆全往金公谅家。仁嫔喃也。方谈笑。山海急奴来曰。大爷垂涕招郎君。公谅怪之。朝往问故。庆全曰。郑相方先请光海储嗣。次杀仁嫔 王子。吾亲何见是。是以泣。公谅告仁嫔。嫔痛哭。 上问之。告其事。愿归死小人家。 上疑之。密以御札。往复山海。且使人密探松江宾客往来者。又使信城外舅申砬。率军官直信城备不虞。松江不知也。(野史)郑松江为奸臣所谗。以为将杀信城母子。 上疑怒。一日。以问公。(信城君。公之婿。)公曰。臣请以百口保之。此不过不悦者欲谗杀耳。澈量虽狭。窃观其心事。真坦荡君子也。(申都巡砬墓碣)
同福丁岩寿。尝往来松江之门者也。时上疏极言李泼,崔永庆事。议或有疑松江者。南东冈彦经与牛溪松思为道义之交。而亦为丁疏所斥。牛溪以汝立相知。上疏自讼。愿与南彦经同被罪罚云。以此推之。松江不知丁疏。昭然可知矣。
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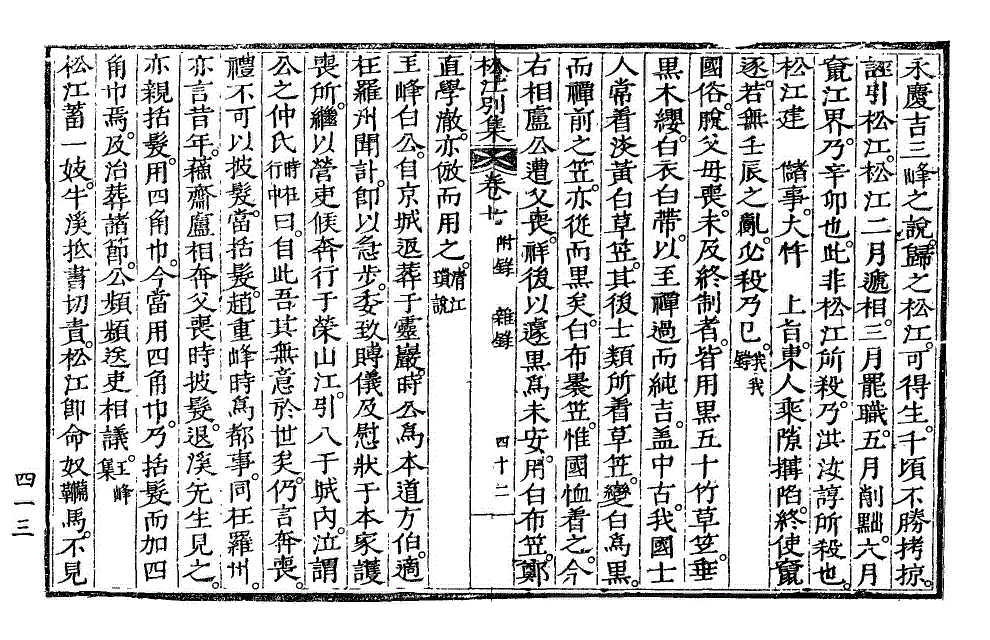 永庆吉三峰之说。归之松江。可得生。千顷不胜拷掠。诬引松江。松江二月递相。三月罢职。五月削黜。六月窜江界。乃辛卯也。此非松江所杀。乃洪汝谆所杀也。松江建 储事。大忤 上旨。东人乘隙搆陷。终使窜逐。若无壬辰之乱。必杀乃已。(我我录)
永庆吉三峰之说。归之松江。可得生。千顷不胜拷掠。诬引松江。松江二月递相。三月罢职。五月削黜。六月窜江界。乃辛卯也。此非松江所杀。乃洪汝谆所杀也。松江建 储事。大忤 上旨。东人乘隙搆陷。终使窜逐。若无壬辰之乱。必杀乃已。(我我录)国俗。脱父母丧。未及终制者。皆用黑五十竹草笠。垂黑木缨。白衣白带。以至禫过而纯吉。盖中古。我国士人常着淡黄白草笠。其后士类所着草笠。变白为黑。而禫前之笠。亦从而黑矣。白布裹笠。惟国恤着之。今右相卢公遭父丧。祥后以遽黑为未安。用白布笠。郑直学澈。亦仿而用之。(清江琐说)
玉峰白公。自京城返葬于灵岩。时公为本道方伯。适在罗州闻讣。即以急步。委致赙仪及慰状于本家护丧所。继以营吏候奔行于荣山江。引入于城内。泣谓公之仲氏(时在行中)曰。自此吾其无意于世矣。仍言奔丧。礼不可以披发。当括发。赵重峰时为都事。同在罗州。亦言昔年。苏斋卢相奔父丧时披发。退溪先生见之。亦亲括发。用四角巾。今当用四角巾。乃括发而加四角巾焉。及治葬诸节。公频频送吏相议。(玉峰集)
松江蓄一妓。牛溪抵书切责。松江即命奴鞴马。不见
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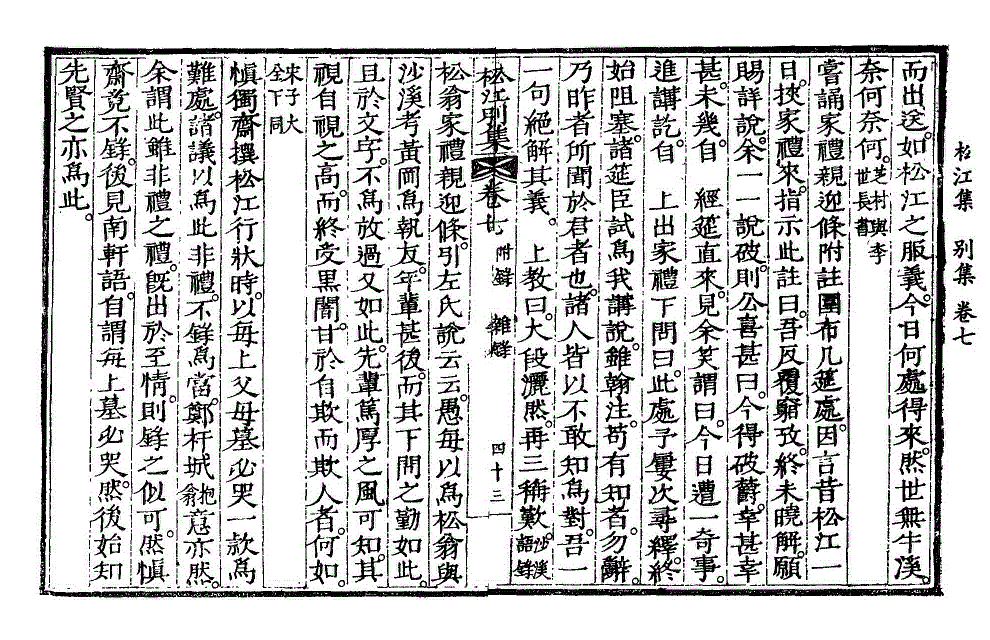 而出送。如松江之服义。今日何处得来。然世无牛溪。奈何奈何。(芝村与李世长书)
而出送。如松江之服义。今日何处得来。然世无牛溪。奈何奈何。(芝村与李世长书)尝诵家礼亲迎条附注围布几筵处。因言昔松江一日。挟家礼来。指示此注曰。吾反覆穷考。终未晓解。愿赐详说。余一一说破。则公喜甚曰。今得破郁。幸甚幸甚。未几。自 经筵直来。见余笑谓曰。今日遭一奇事。进讲讫。自 上出家礼下问曰。此处予屡次寻绎。终始阻塞。诸筵臣试为我讲说。虽翰注。苟有知者。勿辞。乃昨者所闻于君者也。诸人皆以不敢知为对。吾一一句绝解其义。 上教曰。大段洒然。再三称叹。(沙溪语录)
松翁家礼亲迎条。引左氏说云云。愚每以为松翁与沙溪考黄冈为执友。年辈甚后。而其下问之勤如此。且于文字。不为放过又如此。先辈笃厚之风可知。其视自视之高。而终受黑闇。甘于自欺而欺人者。何如。(宋子大全下同)
慎独斋撰松江行状时。以每上父母墓必哭一款为难处。诸议以为此非礼。不录为当。郑杆城(抱翁)意亦然。余谓此虽非礼之礼。既出于至情。则录之似可。然慎斋竟不录。后见南轩语。自谓每上墓必哭。然后始知先贤之亦为此。
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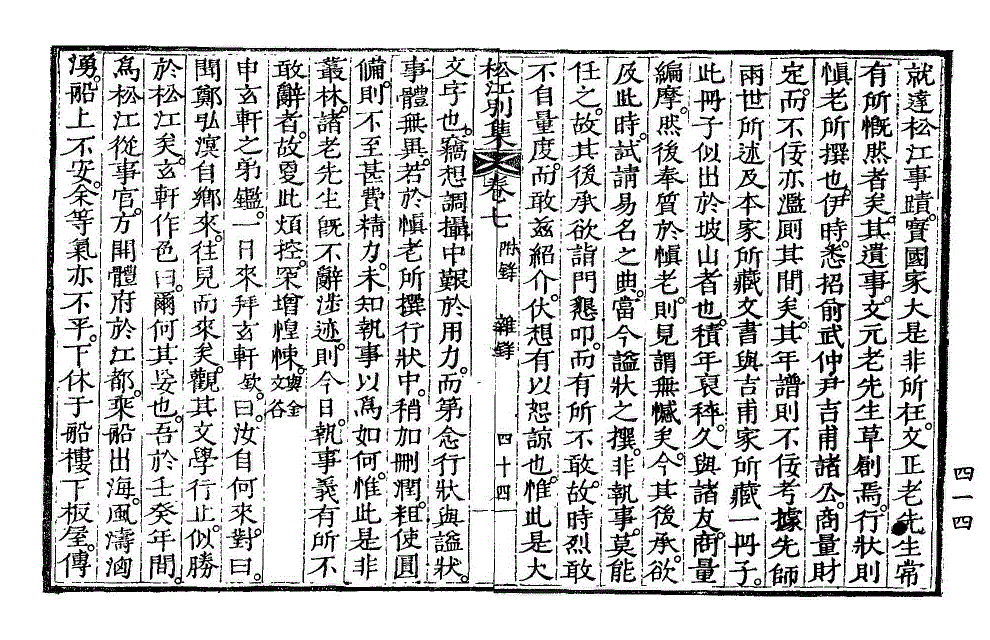 就达松江事迹。实国家大是非所在。文正老先生常有所慨然者矣。其遗事。文元老先生草创焉。行状则慎老所撰也。伊时。悉招俞武仲,尹吉甫诸公。商量财定。而不佞亦滥厕其间矣。其年谱则不佞考据先师两世所述及本家所藏文书与吉甫家所藏一册子。此册子似出于坡山者也。积年裒稡。久与诸友。商量编摩。然后奉质于慎老。则见谓无憾矣。今其后承。欲及此时。试请易名之典。当今谥状之撰。非执事。莫能任之。故其后承欲诣门恳叩。而有所不敢。故时烈敢不自量度。而敢玆绍介。伏想有以恕谅也。惟此是大文字也。窃想调摄中艰于用力。而第念行状与谥状。事体无异。若于慎老所撰行状中。稍加删润。粗使圆备。则不至甚费精力。未知执事以为如何。惟此是非丛林。诸老先生既不辞涉迹。则今日。执事义有所不敢辞者。故更此烦控。深增惶悚。(与金文谷)
就达松江事迹。实国家大是非所在。文正老先生常有所慨然者矣。其遗事。文元老先生草创焉。行状则慎老所撰也。伊时。悉招俞武仲,尹吉甫诸公。商量财定。而不佞亦滥厕其间矣。其年谱则不佞考据先师两世所述及本家所藏文书与吉甫家所藏一册子。此册子似出于坡山者也。积年裒稡。久与诸友。商量编摩。然后奉质于慎老。则见谓无憾矣。今其后承。欲及此时。试请易名之典。当今谥状之撰。非执事。莫能任之。故其后承欲诣门恳叩。而有所不敢。故时烈敢不自量度。而敢玆绍介。伏想有以恕谅也。惟此是大文字也。窃想调摄中艰于用力。而第念行状与谥状。事体无异。若于慎老所撰行状中。稍加删润。粗使圆备。则不至甚费精力。未知执事以为如何。惟此是非丛林。诸老先生既不辞涉迹。则今日。执事义有所不敢辞者。故更此烦控。深增惶悚。(与金文谷)申玄轩之弟鉴。一日来拜玄轩(钦)。曰。汝自何来。对曰。闻郑弘溟自乡来。往见而来矣。观其文学行止。似胜于松江矣。玄轩作色曰。尔何其妄也。吾于壬癸年间。为松江从事官。方开体府于江都。乘船出海。风涛汹涌。船上不安。余等气亦不平。下休于船楼下板屋。传
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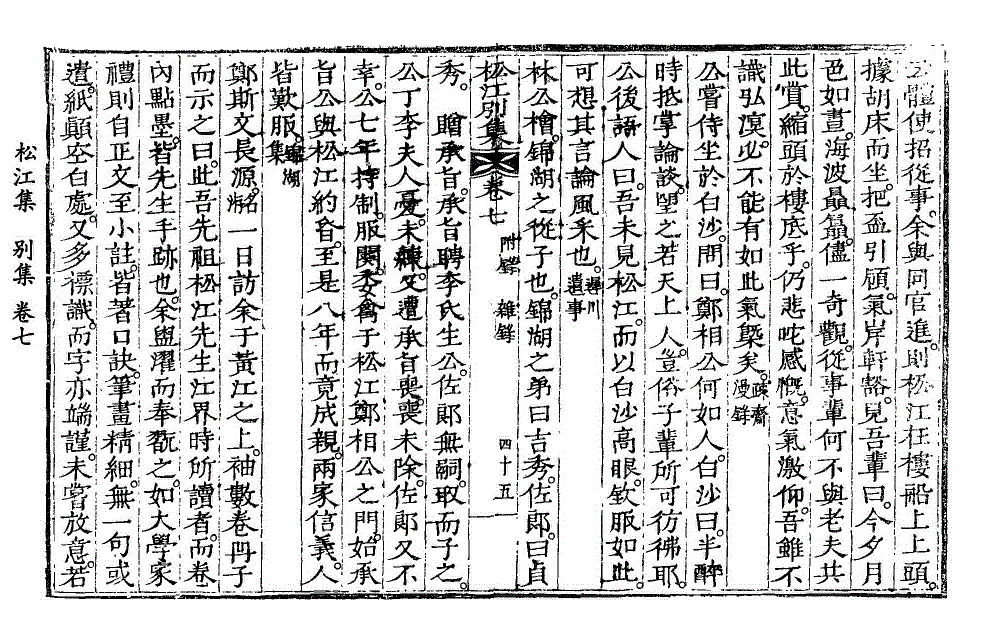 云体使招从事。余与同官进。则松江在楼船上上头。据胡床而坐。把杯引领。气岸轩豁。见吾辈曰。今夕月色如昼。海波赑屃。尽一奇观。从事辈何不与老夫共此赏。缩头于楼底乎。仍悲咜感慨。意气激仰。吾虽不识弘溟。必不能有如此气概矣。(疏斋漫录)
云体使招从事。余与同官进。则松江在楼船上上头。据胡床而坐。把杯引领。气岸轩豁。见吾辈曰。今夕月色如昼。海波赑屃。尽一奇观。从事辈何不与老夫共此赏。缩头于楼底乎。仍悲咜感慨。意气激仰。吾虽不识弘溟。必不能有如此气概矣。(疏斋漫录)公尝侍坐于白沙。问曰。郑相公何如人。白沙曰。半醉时抵掌论谈。望之若天上人。岂俗子辈所可彷佛耶。公后语人曰。吾未见松江。而以白沙高眼。钦服如此。可想其言论风采也。(迟川遗事)
林公桧。锦湖之从子也。锦湖之弟曰吉秀。佐郎。曰贞秀。 赠承旨。承旨聘李氏生公。佐郎无嗣。取而子之。公丁李夫人忧。未练。又遭承旨丧。丧未除。佐郎又不幸。公七年持制。服阕。委禽于松江郑相公之门。始承旨公与松江约昏。至是八年而竟成亲。两家信义。人皆叹服。(锦湖集)
郑斯文长源。(名荐)一日访余于黄江之上。袖数卷册子而示之曰。此吾先祖松江先生江界时所读者。而卷内点墨。皆先生手迹也。余盥濯而奉玩之。如大学,家礼则自正文至小注。皆著口诀。笔画精细。无一句或遗。纸颠空白处。又多标识。而字亦端谨。未尝放意。若
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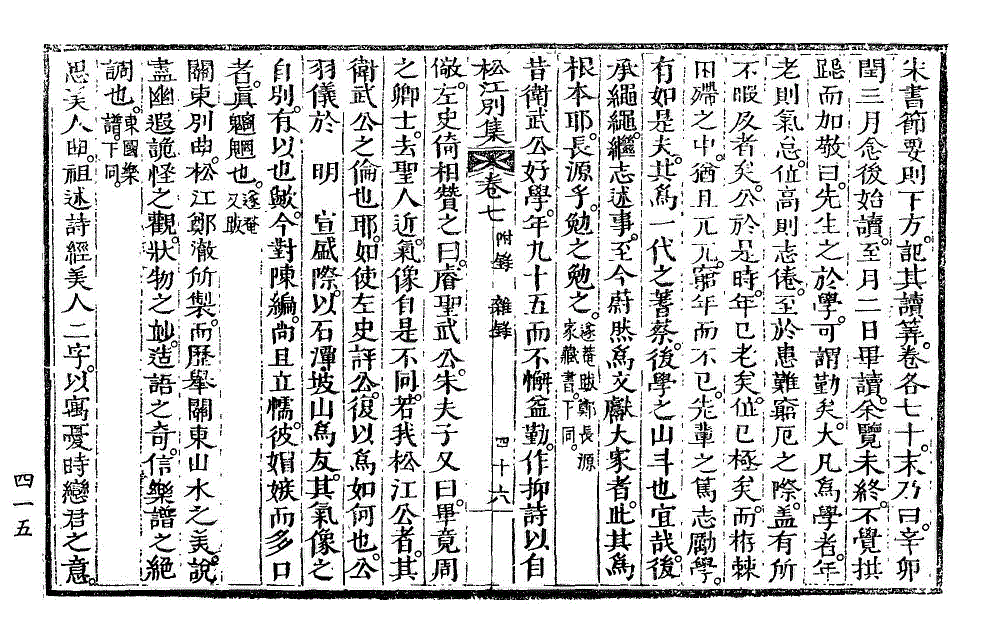 朱书节要则下方。记其读算。卷各七十。末乃曰。辛卯闰三月念后始读。至月二日毕读。余览未终。不觉拱跽而加敬曰。先生之于学。可谓勤矣。大凡为学者。年老则气怠。位高则志倦。至于患难穷厄之际。盖有所不暇及者矣。公于是时。年已老矣。位已极矣。而栫棘困殢之中。犹且兀兀。穷年而不已。先辈之笃志励学。有如是夫。其为一代之蓍蔡。后学之山斗也宜哉。后承绳绳。继志述事。至今蔚然为文献大家者。此其为根本耶。长源乎。勉之勉之。(遂庵跋郑长源家藏书。下同。)
朱书节要则下方。记其读算。卷各七十。末乃曰。辛卯闰三月念后始读。至月二日毕读。余览未终。不觉拱跽而加敬曰。先生之于学。可谓勤矣。大凡为学者。年老则气怠。位高则志倦。至于患难穷厄之际。盖有所不暇及者矣。公于是时。年已老矣。位已极矣。而栫棘困殢之中。犹且兀兀。穷年而不已。先辈之笃志励学。有如是夫。其为一代之蓍蔡。后学之山斗也宜哉。后承绳绳。继志述事。至今蔚然为文献大家者。此其为根本耶。长源乎。勉之勉之。(遂庵跋郑长源家藏书。下同。)昔卫武公好学。年九十五而不懈益勤。作抑诗以自儆。左史倚相赞之曰。睿圣武公。朱夫子又曰。毕竟周之卿士。去圣人近。气像自是不同。若我松江公者。其卫武公之伦也耶。如使左史评公。复以为如何也。公羽仪于 明 宣盛际。以石潭,坡山为友。其气像之自别。有以也欤。今对陈编。尚且立懦。彼媢嫉而多口者。真魑魍也。(遂庵又跋)
关东别曲。松江郑澈所制。而历举关东山水之美。说尽幽遐诡怪之观。状物之妙。造语之奇。信乐谱之绝调也。(东国乐谱。下同。)
思美人曲。祖述诗经美人二字。以寓忧时恋君之意。
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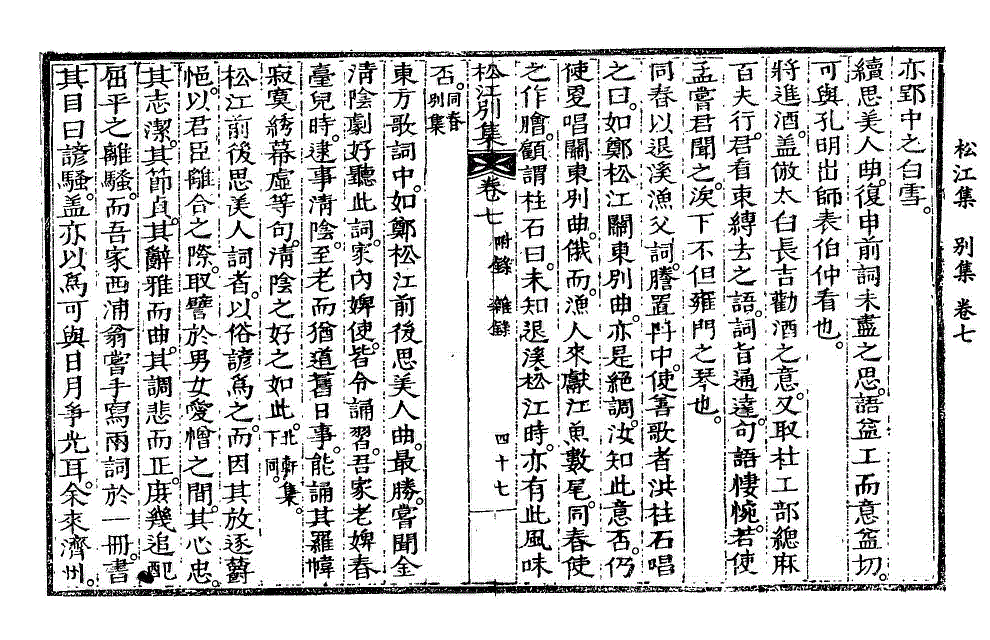 亦郢中之白雪。
亦郢中之白雪。续思美人曲。复申前词未尽之思。语益工而意益切。可与孔明出师表伯仲看也。
将进酒。盖仿太白长吉劝酒之意。又取杜工部缌麻百夫行。君看束缚去之语。词旨通达。句语悽惋。若使孟尝君闻之。泪下不但雍门之琴也。
同春以退溪渔父词。誊置册中。使善歌者洪柱石唱之曰。如郑松江关东别曲。亦是绝调。汝知此意否。仍使更唱关东别曲。俄而。渔人来献江鱼数尾。同春使之作脍。顾谓柱石曰。未知退溪,松江时。亦有此风味否。(同春别集)
东方歌词中。如郑松江前后思美人曲。最胜。尝闻金清阴剧好听此词。家内婢使。皆令诵习。吾家老婢春台儿时。逮事清阴。至老而犹道旧日事。能诵其罗帏寂寞绣幕虚等句。清阴之好之如此。(北轩集。下同。)
松江前后思美人词者。以俗谚为之。而因其放逐郁悒。以君臣离合之际。取譬于男女爱憎之间。其心忠。其志洁。其节贞。其辞雅而曲。其调悲而正。庶几追配屈平之离骚。而吾家西浦翁尝手写两词于一册。书其目曰谚骚。盖亦以为可与日月争光耳。余来济州。
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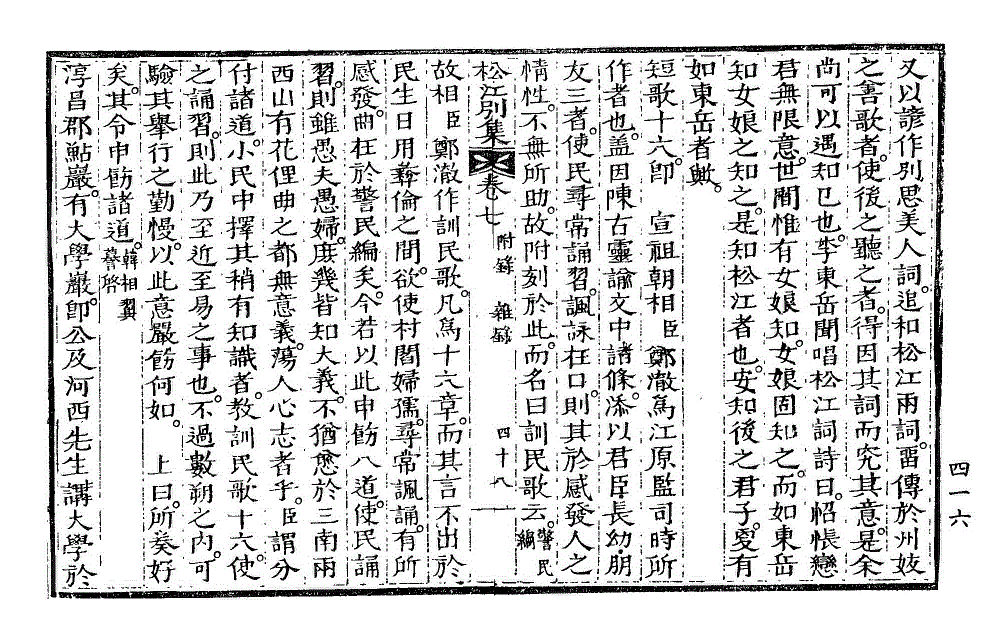 又以谚作别思美人词。追和松江两词。留传于州妓之善歌者。使后之听之者。得因其词而究其意。是余尚可以遇知己也。李东岳闻唱松江词诗曰。怊怅恋君无限意。世间惟有女娘知。女娘固知之。而如东岳知女娘之知之。是知松江者也。安知后之君子。更有如东岳者欤。
又以谚作别思美人词。追和松江两词。留传于州妓之善歌者。使后之听之者。得因其词而究其意。是余尚可以遇知己也。李东岳闻唱松江词诗曰。怊怅恋君无限意。世间惟有女娘知。女娘固知之。而如东岳知女娘之知之。是知松江者也。安知后之君子。更有如东岳者欤。短歌十六。即 宣祖朝相臣郑澈为江原监司时所作者也。盖因陈古灵谕文中诸条。添以君臣,长幼,朋友三者。使民寻常诵习。讽咏在口。则其于感发人之情性。不无所助。故附刻于此。而名曰训民歌云。(警民编)
故相臣郑澈作训民歌。凡为十六章。而其言不出于民生日用彝伦之间。欲使村阎妇孺。寻常讽诵。有所感发。曲在于警民编矣。今若以此申饬八道。使民诵习。则虽愚夫愚妇。庶几皆知大义。不犹愈于三南两西山有花俚曲之都无意义。荡人心志者乎。臣谓分付诸道。小民中择其稍有知识者。教训民歌十六。使之诵习。则此乃至近至易之事也。不过数朔之内。可验其举行之勤慢。以此意严饬何如。 上曰。所奏好矣。其令申饬诸道。(韩相翼谟启)
淳昌郡鲇岩。有大学岩。即公及河西先生讲大学于
松江别集卷之七 第 4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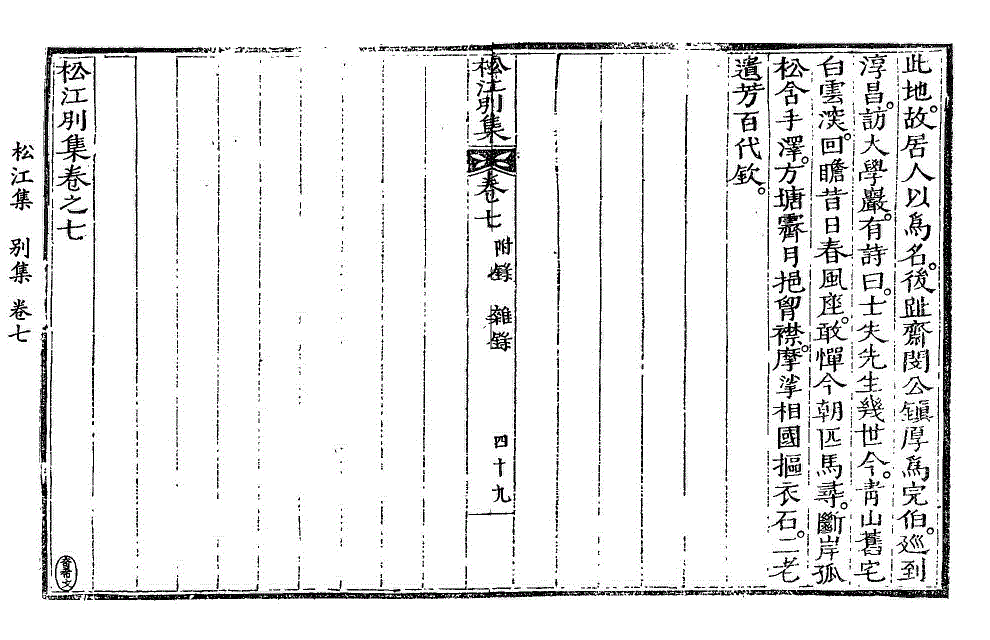 此地。故居人以为名。后趾斋闵公镇厚为完伯。巡到淳昌。访大学岩。有诗曰。士失先生几世今。青山旧宅白云深。回瞻昔日春风座。敢惮今朝匹马寻。断岸孤松含手泽。方塘霁月挹胸襟。摩挲相国抠衣石。二老遗芳百代钦。
此地。故居人以为名。后趾斋闵公镇厚为完伯。巡到淳昌。访大学岩。有诗曰。士失先生几世今。青山旧宅白云深。回瞻昔日春风座。敢惮今朝匹马寻。断岸孤松含手泽。方塘霁月挹胸襟。摩挲相国抠衣石。二老遗芳百代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