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x 页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书
书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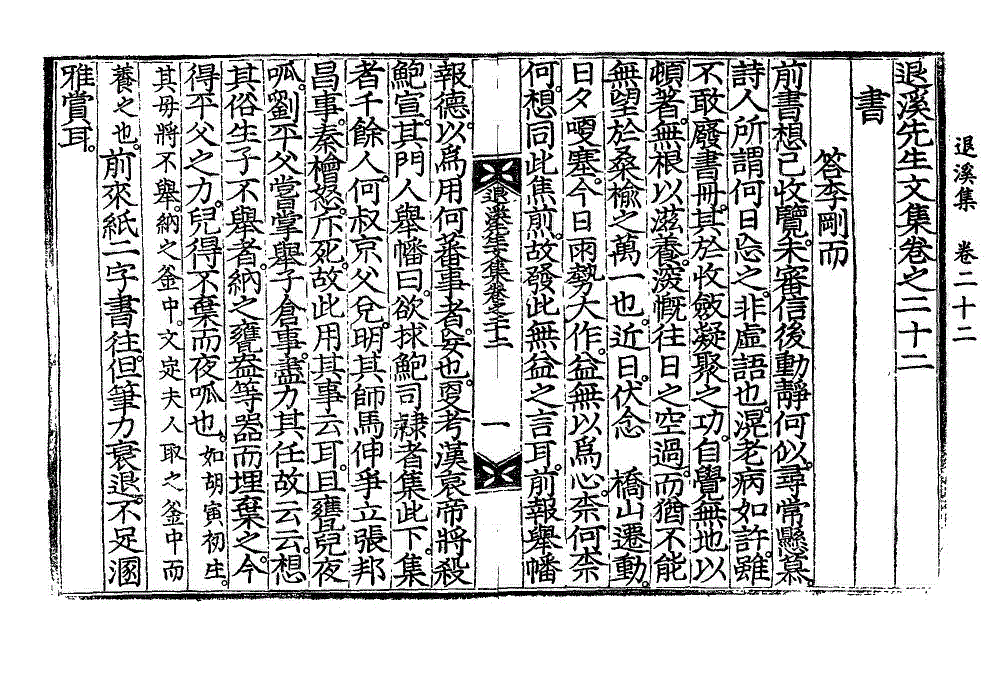 答李刚而
答李刚而前书想已收览。未审信后动静何似。寻常悬慕。诗人所谓何日忘之。非虚语也。滉老病如许。虽不敢废书册。其于收敛凝聚之功。自觉无地以顿著。无根以滋养。深慨往日之空过。而犹不能无望于桑榆之万一也。近日。伏念 桥山迁动。日夕哽塞。今日雨势大作。益无以为心。柰何柰何。想同此焦煎。故发此无益之言耳。前报举幡报德。以为用何蕃事者。妄也。更考汉哀帝将杀鲍宣。其门人举幡曰。欲救鲍司隶者集此下。集者千馀人。何叔京父兑。明其师马伸争立张邦昌事。秦桧怒。斥死。故此用其事云耳。且瓮儿夜呱。刘平父尝掌举子仓事。尽力其任故云云。想其俗生子不举者。纳之瓮盎等器而埋弃之。今得平父之力。儿得不弃而夜呱也。(如胡寅初生。其母将不举。纳之釜中。文定夫人取之釜中而养之也。)前来纸二字书往。但笔力衰退。不足溷雅赏耳。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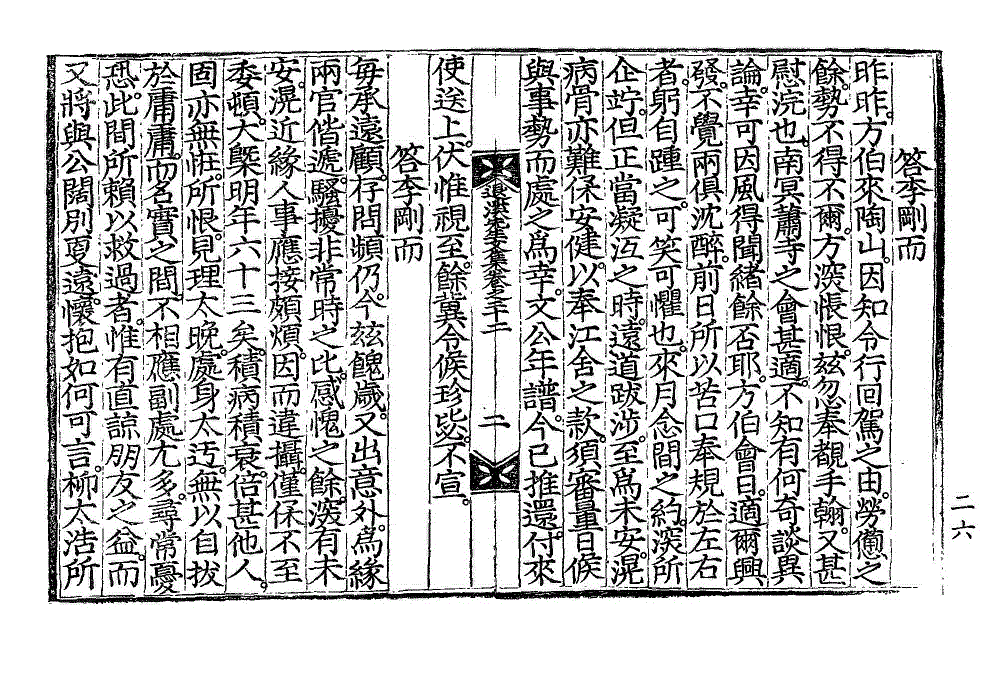 答李刚而
答李刚而昨昨。方伯来陶山。因知令行回驾之由。劳惫之馀。势不得不尔。方深怅恨。玆忽奉睹手翰。又甚慰浣也。南冥萧寺之会甚适。不知有何奇谈异论。幸可因风得闻绪馀否耶。方伯会日。适尔兴发。不觉两俱沈醉。前日所以苦口奉规于左右者。躬自踵之。可笑可惧也。来月念间之约。深所企伫。但正当凝冱之时。远道跋涉。至为未安。滉病骨亦难保安健。以奉江舍之款。须审量日候与事势而处之为幸。文公年谱。今已推还。付来使送上。伏惟视至。馀冀令候珍毖。不宣。
答李刚而
每承远顾。存问频仍。今玆馈岁。又出意外。为缘两官偕递。骚扰非常时之比。感愧之馀。深有未安。滉近缘人事应接颇烦。因而违摄。仅保不至委顿。大槩明年六十三矣。积病积衰。倍甚他人。固亦无怪。所恨。见理太晚。处身太迂。无以自拔于庸庸。而名实之间。不相应副处尤多。寻常忧恐。此间所赖以救过者。惟有直谅朋友之益。而又将与公阔别更远。怀抱如何可言。柳太浩所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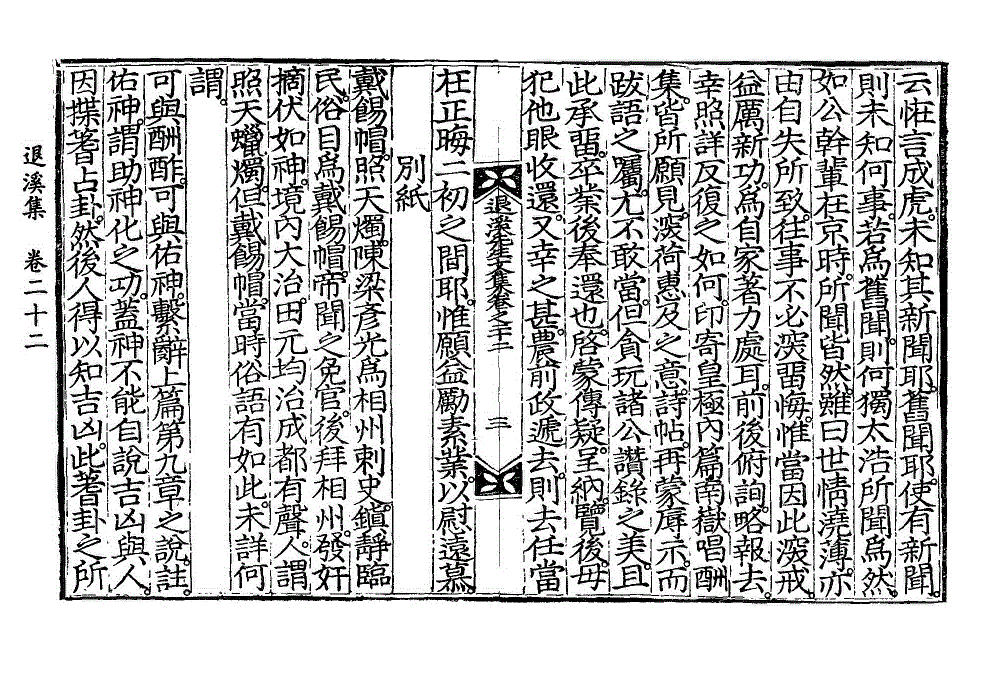 云怪言成虎。未知其新闻耶。旧闻耶。使有新闻。则未知何事。若为旧闻。则何独太浩所闻为然。如公干辈在京时。所闻皆然。虽曰世情浇薄。亦由自失所致。往事不必深留悔。惟当因此深戒。益厉新功。为自家著力处耳。前后俯询。略报去。幸照详反复之如何。印寄皇极内篇,南岳唱酬集。皆所愿见。深荷惠及之意。诗帖。再蒙辱示。而跋语之嘱。尤不敢当。但贪玩诸公赞录之美。且此承留。卒业后奉还也。启蒙传疑。呈纳。览后。毋犯他眼收还。又幸之甚。农前政递去。则去任当在正晦二初之间耶。惟愿益励素业。以慰远慕。
云怪言成虎。未知其新闻耶。旧闻耶。使有新闻。则未知何事。若为旧闻。则何独太浩所闻为然。如公干辈在京时。所闻皆然。虽曰世情浇薄。亦由自失所致。往事不必深留悔。惟当因此深戒。益厉新功。为自家著力处耳。前后俯询。略报去。幸照详反复之如何。印寄皇极内篇,南岳唱酬集。皆所愿见。深荷惠及之意。诗帖。再蒙辱示。而跋语之嘱。尤不敢当。但贪玩诸公赞录之美。且此承留。卒业后奉还也。启蒙传疑。呈纳。览后。毋犯他眼收还。又幸之甚。农前政递去。则去任当在正晦二初之间耶。惟愿益励素业。以慰远慕。别纸
戴饧帽。照天烛。陈梁彦光为相州刺史。镇静临民。俗目为戴饧帽。帝闻之免官。后拜相州。发奸摘伏如神。境内大治。田元均治成都有声。人谓照天蜡烛。但戴饧帽。当时俗语有如此。未详何谓。
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系辞上篇第九章之说。注。佑神。谓助神化之功。盖神不能自说吉凶与人。因揲蓍占卦。然后人得以知吉凶。此蓍卦之所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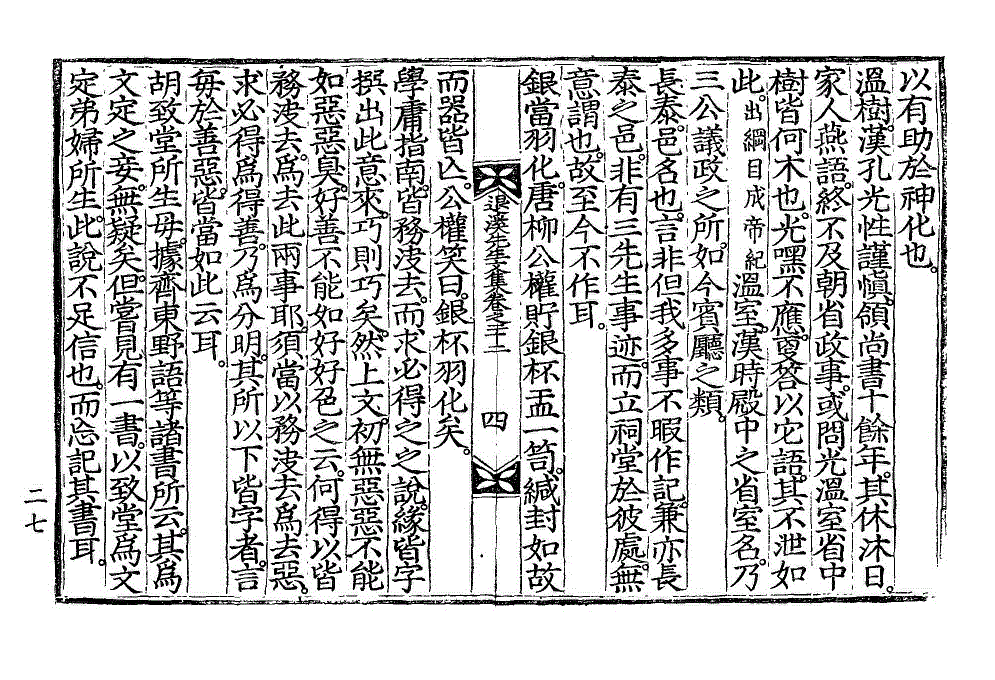 以有助于神化也。
以有助于神化也。温树。汉孔光性谨慎。领尚书十馀年。其休沐日。家人燕语。终不及朝省政事。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嘿不应。更答以它语。其不泄如此。(出纲目成帝纪)温室。汉时殿中之省室名。乃三公议政之所。如今宾厅之类。
长泰。邑名也。言非但我多事不暇作记。兼亦长泰之邑。非有三先生事迹。而立祠堂于彼处。无意谓也。故至今不作耳。
银当羽化。唐柳公权贮银杯盂一笥。缄封如故而器皆亡。公权笑曰。银杯羽化矣。
学庸指南。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之说。缘皆字撰出此意来。巧则巧矣。然上文。初无恶恶不能如恶恶臭。好善不能如好好色之云。何得以皆务决去。为去此两事耶。须当以务决去为去恶。求必得为得善。乃为分明。其所以下皆字者。言每于善恶。皆当如此云耳。
胡致堂所生母。据齐东野语等诸书所云。其为文定之妾。无疑矣。但尝见有一书。以致堂为文定弟妇所生。此说不足信也。而忘记其书耳。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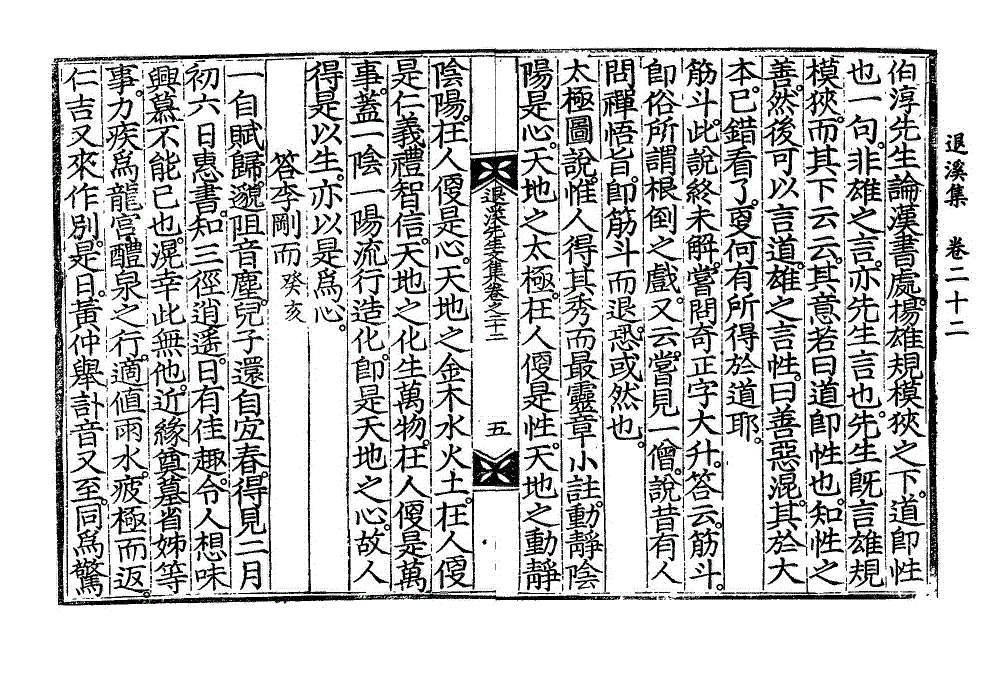 伯淳先生论汉书处。扬雄规模狭之下。道即性也一句。非雄之言。亦先生言也。先生既言雄规模狭。而其下云云。其意若曰道即性也。知性之善。然后可以言道。雄之言性。曰善恶混。其于大本。已错看了。更何有所得于道耶。
伯淳先生论汉书处。扬雄规模狭之下。道即性也一句。非雄之言。亦先生言也。先生既言雄规模狭。而其下云云。其意若曰道即性也。知性之善。然后可以言道。雄之言性。曰善恶混。其于大本。已错看了。更何有所得于道耶。筋斗。此说终未解。尝问奇正字大升。答云。筋斗。即俗所谓根倒之戏。又云。尝见一僧。说昔有人问禅悟旨。即筋斗而退。恐或然也。
太极图说。惟人得其秀而最灵章小注。动静阴阳是心。天地之太极。在人便是性。天地之动静阴阳。在人便是心。天地之金木水火土。在人便是仁义礼智信。天地之化生万物。在人便是万事。盖一阴一阳流行造化。即是天地之心。故人得是以生。亦以是为心。
答李刚而(癸亥)
一自赋归。邈阻音尘。儿子还自宜春。得见二月初六日惠书。知三径逍遥。日有佳趣。令人想味兴慕不能已也。滉幸此无他。近缘奠墓省姊等事。力疾为龙宫,醴泉之行。适值雨水。疲极而返。仁吉又来作别。是日。黄仲举讣音又至。同为惊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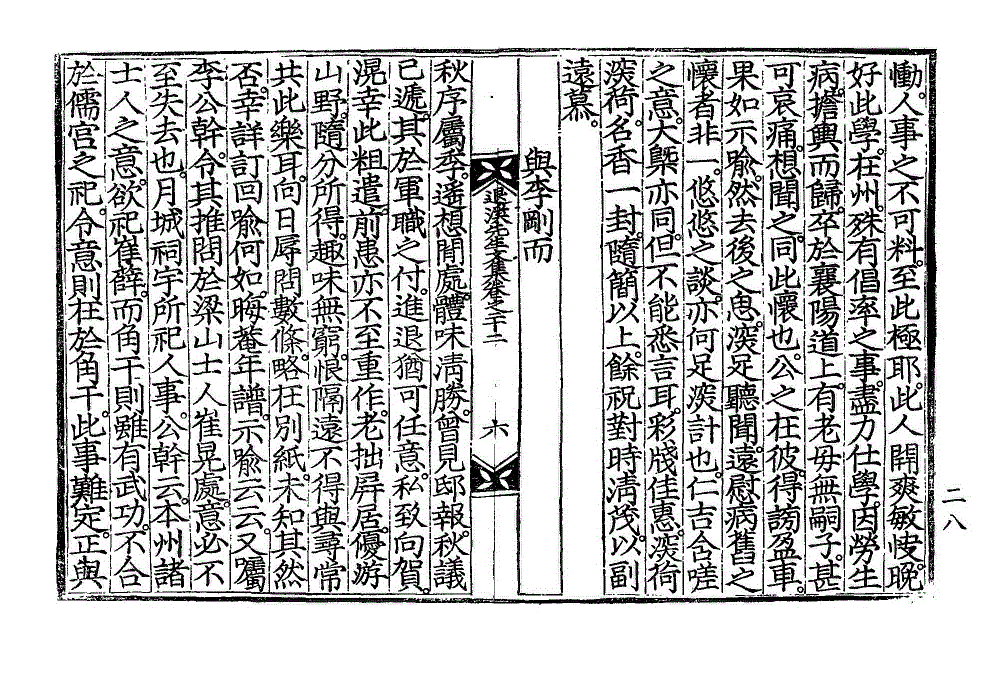 恸。人事之不可料。至此极耶。此人开爽敏快。晚好此学。在州。殊有倡率之事。尽力仕学。因劳生病。担舆而归。卒于襄阳道上。有老母无嗣子。甚可哀痛。想闻之。同此怀也。公之在彼。得谤盈车。果如示喻。然去后之思。深足听闻。远慰病旧之怀者非一。悠悠之谈。亦何足深计也。仁吉含嗟之意。大槩亦同。但不能悉言耳。彩笺佳惠。深荷深荷。名香一封。随简以上。馀祝对时清茂。以副远慕。
恸。人事之不可料。至此极耶。此人开爽敏快。晚好此学。在州。殊有倡率之事。尽力仕学。因劳生病。担舆而归。卒于襄阳道上。有老母无嗣子。甚可哀痛。想闻之。同此怀也。公之在彼。得谤盈车。果如示喻。然去后之思。深足听闻。远慰病旧之怀者非一。悠悠之谈。亦何足深计也。仁吉含嗟之意。大槩亦同。但不能悉言耳。彩笺佳惠。深荷深荷。名香一封。随简以上。馀祝对时清茂。以副远慕。与李刚而
秋序属季。遥想閒处。体味清胜。曾见邸报。秋议已递。其于军职之付。进退犹可任意。私致向贺。滉幸此粗遣。前患亦不至重作。老拙屏居。优游山野。随分所得。趣味无穷。恨隔远不得与寻常共此乐耳。向日辱问数条。略在别纸。未知其然否。幸详订回喻何如。晦庵年谱。示喻云云。又嘱李公干。令其推问于梁山士人崔晃处。意必不至失去也。月城祠宇所祀人事。公干云。本州诸士人之意。欲祀崔,薛。而角干则虽有武功。不合于儒宫之祀。令意则在于角干。此事难定。正与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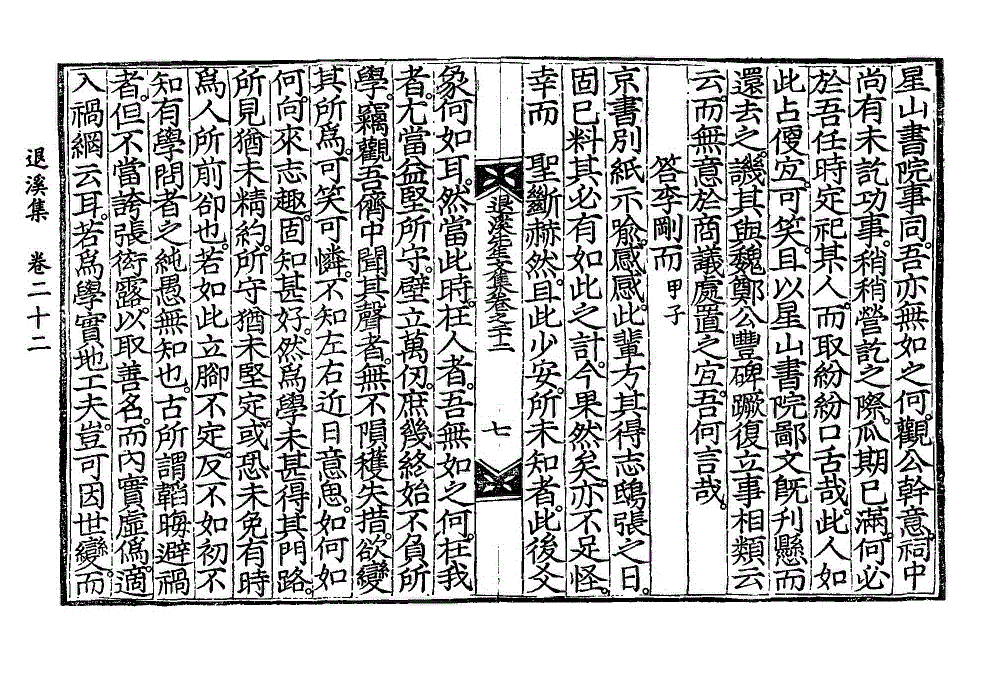 星山书院事同。吾亦无如之何。观公干意。祠中尚有未讫功事。稍稍营讫之际。瓜期已满。何必于吾任时定祀某人。而取纷纷口舌哉。此人如此占便宜。可笑。且以星山书院鄙文既刊悬而还去之。讥其与魏郑公丰碑蹶复立事相类云云。而无意于商议处置之宜。吾何言哉。
星山书院事同。吾亦无如之何。观公干意。祠中尚有未讫功事。稍稍营讫之际。瓜期已满。何必于吾任时定祀某人。而取纷纷口舌哉。此人如此占便宜。可笑。且以星山书院鄙文既刊悬而还去之。讥其与魏郑公丰碑蹶复立事相类云云。而无意于商议处置之宜。吾何言哉。答李刚而(甲子)
京书别纸示喻。感感。此辈方其得志鸱张之日。固已料其必有如此之计。今果然矣。亦不足怪。幸而 圣断赫然。且此少安。所未知者。此后爻象何如耳。然当此时。在人者。吾无如之何。在我者。尤当益坚所守。壁立万仞。庶几终始不负所学。窃观吾侪中闻其声者。无不陨穫失措。欲变其所为。可笑可怜。不知左右近日意思。如何如何。向来志趣。固知甚好。然为学未甚得其门路。所见犹未精约。所守犹未坚定。或恐未免有时为人所前却也。若如此立脚不定。反不如初不知有学问者之纯愚无知也。古所谓韬晦避祸者。但不当誇张衒露。以取善名。而内实虚伪。适入祸网云耳。若为学实地工夫。岂可因世变。而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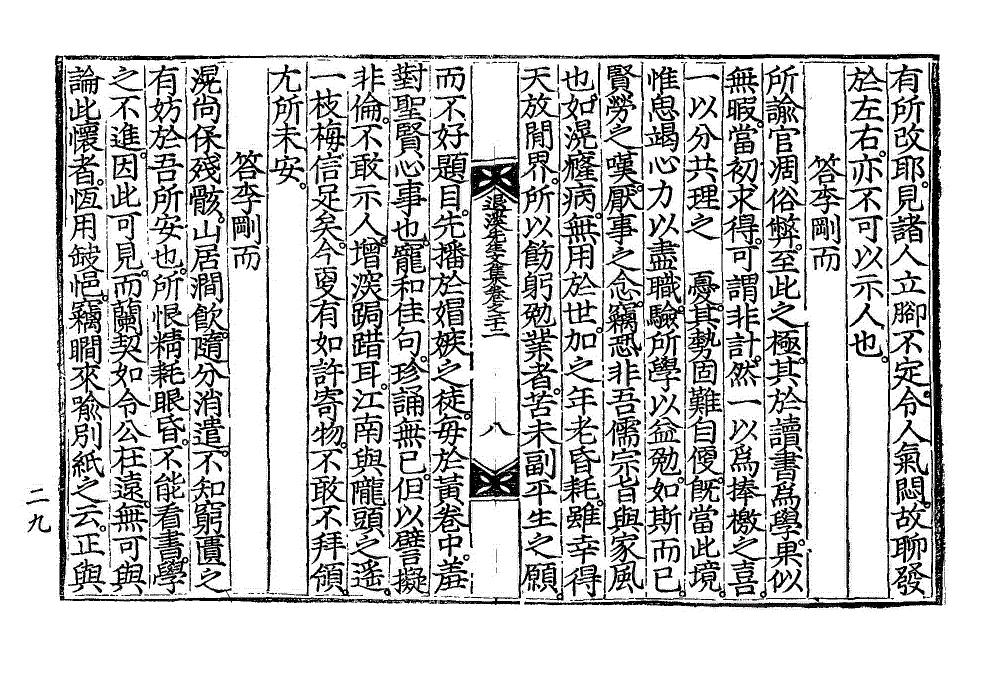 有所改耶。见诸人立脚不定。令人气闷。故聊发于左右。亦不可以示人也。
有所改耶。见诸人立脚不定。令人气闷。故聊发于左右。亦不可以示人也。答李刚而
所谕官凋俗弊。至此之极。其于读书为学。果似无暇。当初求得。可谓非计。然一以为捧檄之喜。一以分共理之 忧。其势固难自便。既当此境。惟思竭心力以尽职。验所学以益勉。如斯而已。贤劳之叹。厌事之念。窃恐非吾儒宗旨与家风也。如滉癃病。无用于世。加之年老昏耗。虽幸得天放閒界。所以饬躬勉业者。苦未副平生之愿。而不好题目。先播于媢嫉之徒。每于黄卷中。羞对圣贤心事也。宠和佳句。珍诵无已。但以譬拟非伦。不敢示人。增深跼踖耳。江南与陇头之遥。一枝梅信足矣。今更有如许寄物。不敢不拜领。尤所未安。
答李刚而
滉尚保残骸。山居涧饮。随分消遣。不知穷匮之有妨于吾所安也。所恨精耗眼昏。不能看书。学之不进。因此可见。而兰契如令公在远。无可与论此怀者。恒用缺悒。窃瞷来喻别纸之云。正与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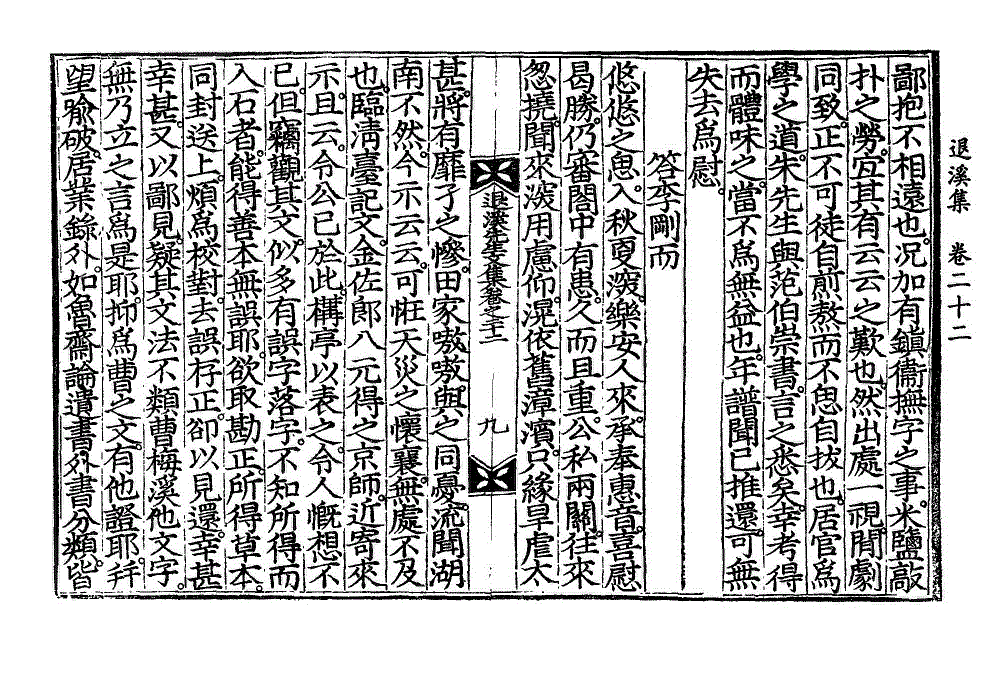 鄙抱不相远也。况加有镇卫抚字之事。米盐敲扑之劳。宜其有云云之叹也。然出处一视。閒剧同致。正不可徒自煎熬而不思自拔也。居官为学之道。朱先生与范伯崇书。言之悉矣。幸考得而体味之。当不为无益也。年谱闻已推还。可无失去为慰。
鄙抱不相远也。况加有镇卫抚字之事。米盐敲扑之劳。宜其有云云之叹也。然出处一视。閒剧同致。正不可徒自煎熬而不思自拔也。居官为学之道。朱先生与范伯崇书。言之悉矣。幸考得而体味之。当不为无益也。年谱闻已推还。可无失去为慰。答李刚而
悠悠之思。入秋更深。乐安人来。承奉惠音。喜慰曷胜。仍审閤中有患。久而且重。公私两关。往来悤挠。闻来深用虑仰。滉依旧漳滨。只缘旱虐太甚。将有靡孑之惨。田家嗷嗷。与之同忧。流闻湖南不然。今示云云。可怪天灾之怀襄。无处不及也。临清台记文。金佐郎八元得之京师。近寄来示。且云。令公已于此。构亭以表之。令人慨想不已。但窃观其文。似多有误字落字。不知所得而入石者。能得善本无误耶。欲取勘正。所得草本。同封送上。烦为校对。去误存正。却以见还。幸甚幸甚。又以鄙见。疑其文法不类曹梅溪他文字。无乃立之言为是耶。抑为曹之文。有他證耶。并望喻破。居业录外。如鲁斋论,遗书。外书分类。皆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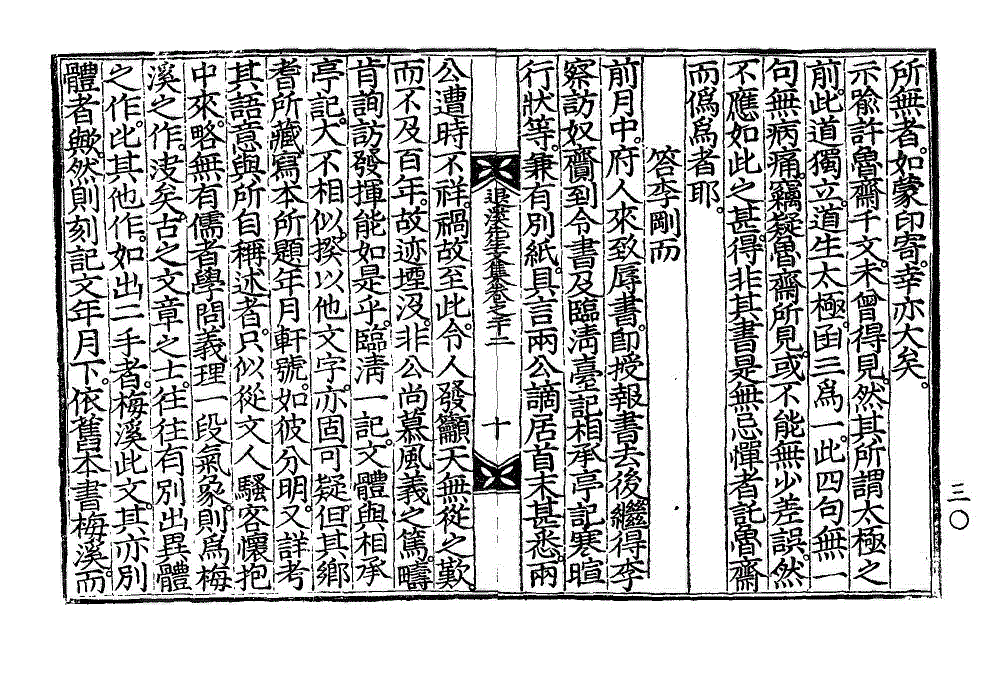 所无者。如蒙印寄。幸亦大矣。
所无者。如蒙印寄。幸亦大矣。示喻许鲁斋千文。未曾得见。然其所谓太极之前。此道独立。道生太极。函三为一。此四句无一句无病痛。窃疑鲁斋所见。或不能无少差误。然不应如此之甚。得非其书是无忌惮者托鲁斋而伪为者耶。
答李刚而
前月中。府人来致辱书。即授报书去后。继得李察访奴赍到令书及临清台记,相承亭记,寒暄行状等。兼有别纸。具言两公谪居首末甚悉。两公遭时不祥。祸故至此。令人发吁天无从之叹。而不及百年。故迹堙没。非公尚慕风义之笃。畴肯询访发挥能如是乎。临清一记。文体与相承亭记。大不相似。揆以他文字。亦固可疑。但其乡耆所藏写本所题年月轩号。如彼分明。又详考其语意与所自称述者。只似从文人骚客怀抱中来。略无有儒者学问义理一段气象。则为梅溪之作。决矣。古之文章之士。往往有别出异体之作。比其他作。如出二手者。梅溪此文。其亦别体者欤。然则刻记文年月下。依旧本书梅溪。而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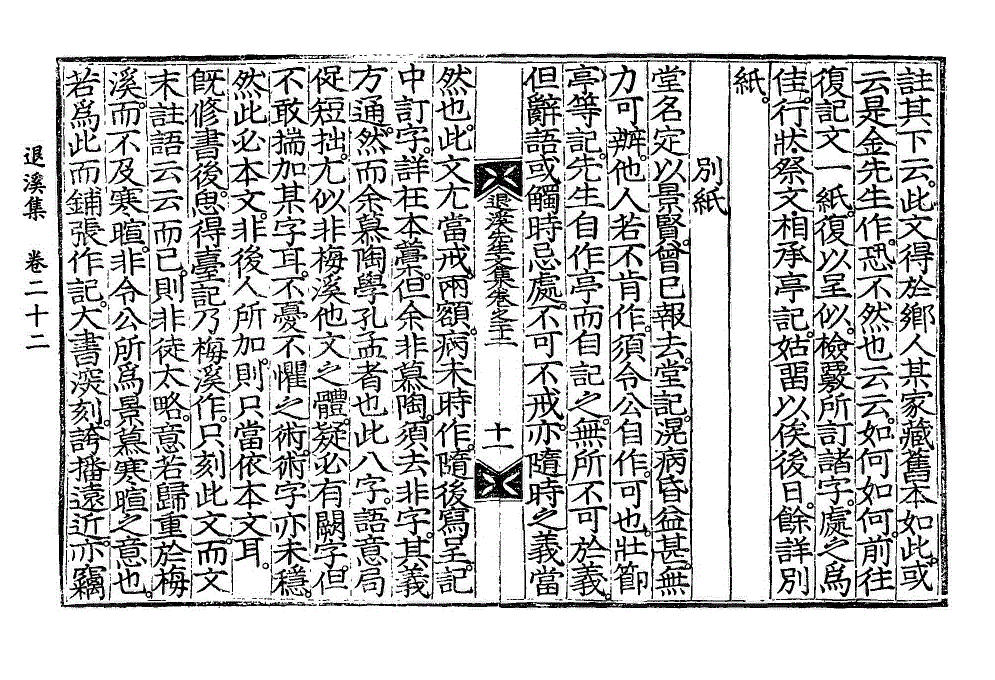 注其下云。此文得于乡人某家藏旧本如此。或云是金先生作。恐不然也云云。如何如何。前往复记文一纸。复以呈似。检覈所订诸字。处之为佳。行状,祭文,相承亭记。姑留以俟后日。馀详别纸。
注其下云。此文得于乡人某家藏旧本如此。或云是金先生作。恐不然也云云。如何如何。前往复记文一纸。复以呈似。检覈所订诸字。处之为佳。行状,祭文,相承亭记。姑留以俟后日。馀详别纸。别纸
堂名定以景贤。曾已报去。堂记。滉病昏益甚。无力可办。他人若不肯作。须令公自作。可也。壮节亭等记。先生自作亭而自记之。无所不可于义。但辞语或触时忌处。不可不戒。亦随时之义当然也。此文尤当戒。两额。病未时作。随后写呈。记中订字。详在本藁。但余非慕陶。须去非字。其义方通。然而余慕陶学孔孟者也此八字。语意局促短拙。尤似非梅溪他文之体。疑必有阙字。但不敢揣加某字耳。不忧不惧之术。术字亦未稳。然此必本文。非后人所加。则只当依本文耳。
既修书后。思得台记乃梅溪作。只刻此文。而文末注语云云而已。则非徒太略。意若归重于梅溪。而不及寒暄。非令公所为景慕寒暄之意也。若为此而铺张作记。大书深刻。誇播远近。亦窃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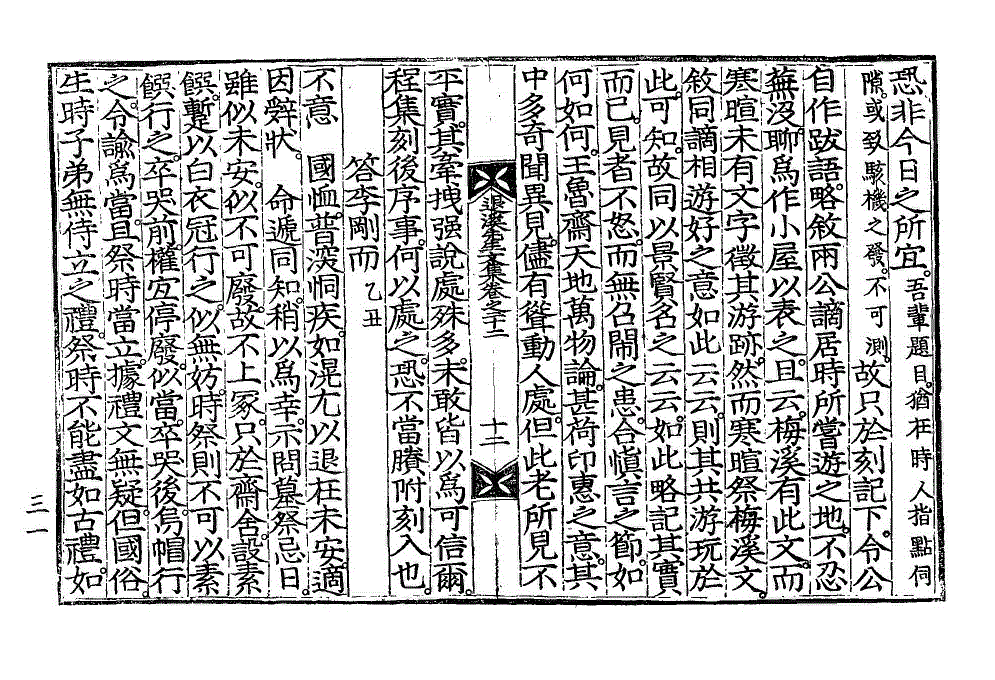 恐非今日之所宜。(吾辈题目。犹在时人指点伺隙。或致骇机之发。不可测。)故只于刻记下。令公自作跋语。略叙两公谪居时所尝游之地。不忍芜没。聊为作小屋以表之。且云。梅溪有此文。而寒暄未有文字徵其游迹。然而寒暄祭梅溪文。叙同谪相游好之意如此云云。则其共游玩于此。可知。故同以景贤名之云云。如此略记其实而已。见者不怒。而无召闹之患。合慎言之节。如何如何。王鲁斋天地万物论。甚荷印惠之意。其中多奇闻异见。尽有耸动人处。但此老所见不平实。其牵拽强说处殊多。未敢皆以为可信尔。程集刻后序事。何以处之。恐不当剩附刻入也。
恐非今日之所宜。(吾辈题目。犹在时人指点伺隙。或致骇机之发。不可测。)故只于刻记下。令公自作跋语。略叙两公谪居时所尝游之地。不忍芜没。聊为作小屋以表之。且云。梅溪有此文。而寒暄未有文字徵其游迹。然而寒暄祭梅溪文。叙同谪相游好之意如此云云。则其共游玩于此。可知。故同以景贤名之云云。如此略记其实而已。见者不怒。而无召闹之患。合慎言之节。如何如何。王鲁斋天地万物论。甚荷印惠之意。其中多奇闻异见。尽有耸动人处。但此老所见不平实。其牵拽强说处殊多。未敢皆以为可信尔。程集刻后序事。何以处之。恐不当剩附刻入也。答李刚而(乙丑)
不意 国恤。普深恫疾。如滉尤以退在未安。适因辞状。 命递同知。稍以为幸。示问墓祭忌日。虽似未安。似不可废。故不上冢。只于斋舍。设素馔。暂以白衣冠行之。似无妨。时祭则不可以素馔行之。卒哭前。权宜停废。似当。卒哭后。乌帽行之。令谕为当。且祭时当立。据礼文无疑。但国俗。生时子弟无侍立之礼。祭时不能尽如古礼。如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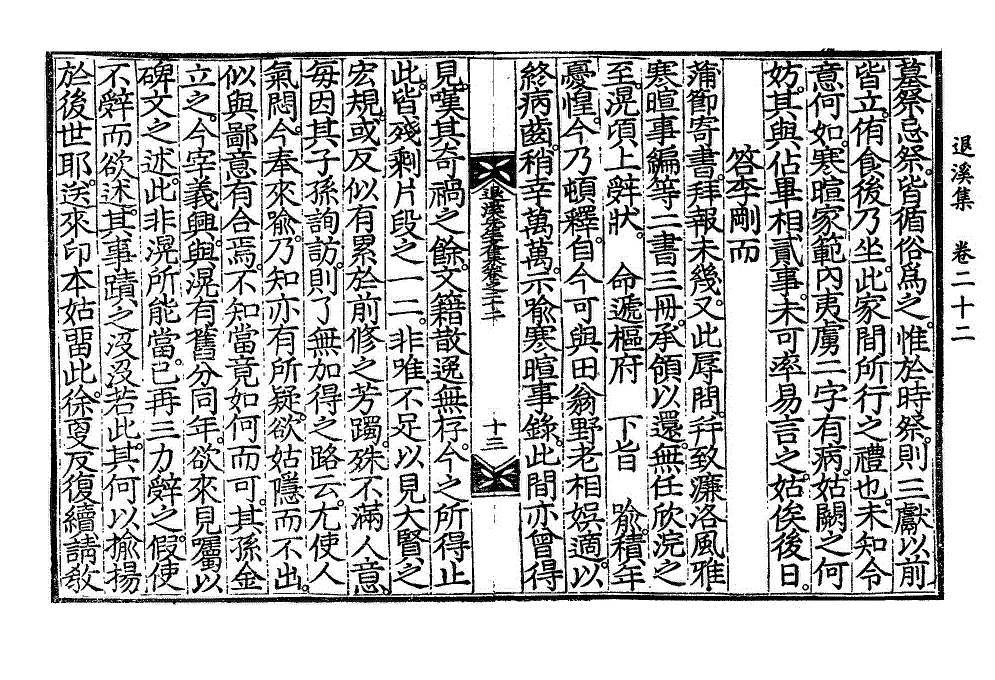 墓祭,忌祭。皆循俗为之。惟于时祭。则三献以前皆立。侑食后乃坐。此家间所行之礼也。未知令意何如。寒暄家范内夷虏二字有病。姑阙之何妨。其与佔毕相贰事。未可率易言之。姑俟后日。
墓祭,忌祭。皆循俗为之。惟于时祭。则三献以前皆立。侑食后乃坐。此家间所行之礼也。未知令意何如。寒暄家范内夷虏二字有病。姑阙之何妨。其与佔毕相贰事。未可率易言之。姑俟后日。答李刚而
蒲节寄书。拜报未几。又此辱问。并致濂洛风雅,寒暄事编等二书三册。承领以还。无任欣浣之至。滉顷上辞状。 命递枢府 下旨 喻。积年忧惶。今乃顿释。自今可与田翁野老相娱适。以终病齿。稍幸万万。示喻寒暄事录。此间亦曾得见。叹其奇祸之馀。文籍散逸无存。今之所得止此。皆残剩片段之一二。非唯不足以见大贤之宏规。或反似有累于前修之芳躅。殊不满人意。每因其子孙询访。则了无加得之路云。尤使人气闷。今奉来喻。乃知亦有所疑。欲姑隐而不出。似与鄙意有合焉。不知当竟如何而可。其孙金立之。今宰义兴。与滉有旧分同年。欲来见嘱以碑文之述。此非滉所能当。已再三力辞之。假使不辞而欲述。其事迹之没没若此。其何以揄扬于后世耶。送来印本姑留此。徐更反复续请教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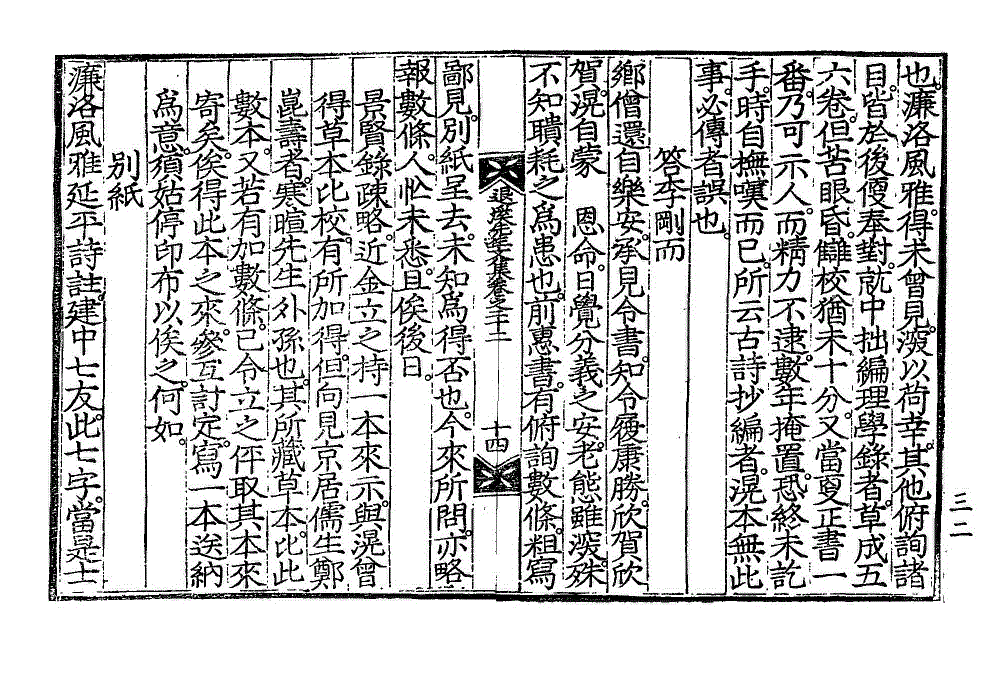 也。濂洛风雅。得未曾见。深以荷幸。其他俯询诸目。皆于后便奉对。就中拙编理学录者。草成五六卷。但苦眼昏。雠校犹未十分。又当更正书一番。乃可示人。而精力不逮。数年掩置。恐终未讫手。时自抚叹而已。所云古诗抄编者。滉本无此事。必传者误也。
也。濂洛风雅。得未曾见。深以荷幸。其他俯询诸目。皆于后便奉对。就中拙编理学录者。草成五六卷。但苦眼昏。雠校犹未十分。又当更正书一番。乃可示人。而精力不逮。数年掩置。恐终未讫手。时自抚叹而已。所云古诗抄编者。滉本无此事。必传者误也。答李刚而
乡僧还自乐安。承见令书。知令履康胜。欣贺欣贺。滉自蒙 恩命。日觉分义之安。老态虽深。殊不知聩耗之为患也。前惠书。有俯询数条。粗写鄙见。别纸呈去。未知为得否也。今来所问。亦略报数条。人忙未悉。且俟后日。
景贤录疏略。近金立之持一本来示。与滉曾得草本比校。有所加得。但向见京居儒生郑昆寿者。寒暄先生外孙也。其所藏草本。比此数本。又若有加数条。已令立之伻取其本来寄矣。俟得此本之来。参互订定。写一本送纳为意。须姑停印布以俟之。何如。
别纸
濂洛风雅延平诗注。建中七友。此七字。当是士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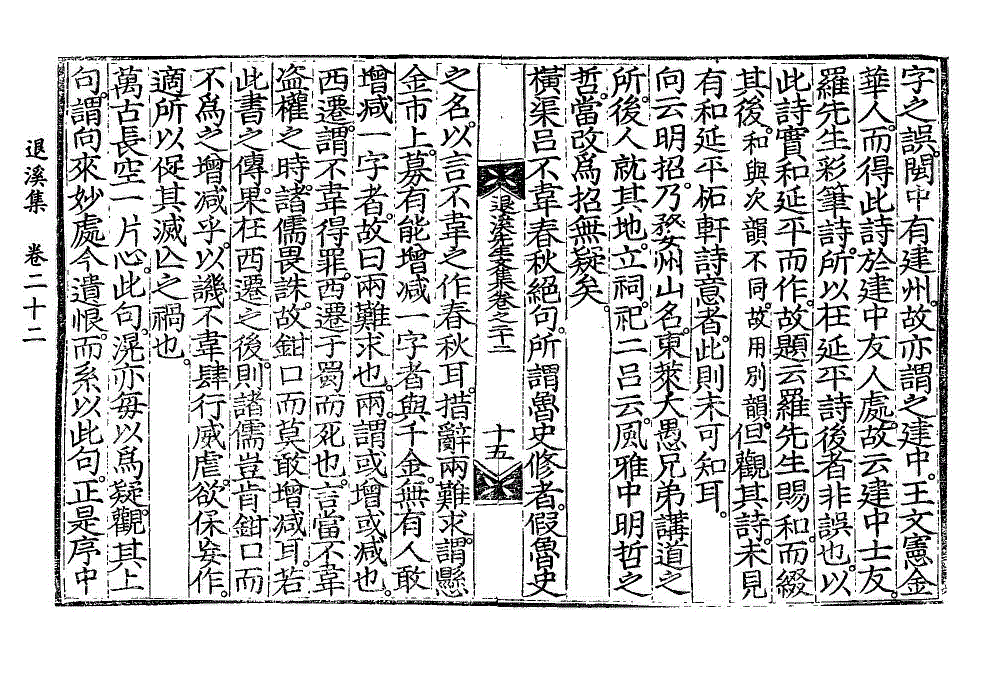 字之误。闽中有建州。故亦谓之建中。王文宪金华人。而得此诗于建中友人处。故云建中士友。罗先生彩笔诗。所以在延平诗后者非误也。以此诗实和延平而作。故题云罗先生赐和。而缀其后。(和与次韵不同。故用别韵。)但观其诗。未见有和延平柘轩诗意者。此则未可知耳。
字之误。闽中有建州。故亦谓之建中。王文宪金华人。而得此诗于建中友人处。故云建中士友。罗先生彩笔诗。所以在延平诗后者非误也。以此诗实和延平而作。故题云罗先生赐和。而缀其后。(和与次韵不同。故用别韵。)但观其诗。未见有和延平柘轩诗意者。此则未可知耳。向云明招。乃婺州山名。东莱,大愚兄弟讲道之所。后人就其地。立祠。祀二吕云。风雅中明哲之哲。当改为招无疑矣。
横渠吕不韦春秋绝句。所谓鲁史修者。假鲁史之名。以言不韦之作春秋耳。措辞两难求。谓悬金市上。募有能增减一字者与千金。无有人敢增减一字者。故曰两难求也。两。谓或增或减也。西迁。谓不韦得罪。西迁于蜀而死也。言当不韦盗权之时。诸儒畏诛。故钳口而莫敢增减耳。若此书之传。果在西迁之后。则诸儒岂肯钳口而不为之增减乎。以讥不韦肆行威虐。欲保妄作。适所以促其灭亡之祸也。
万古长空一片心。此句。滉亦每以为疑。观其上句。谓向来妙处今遗恨。而系以此句。正是序中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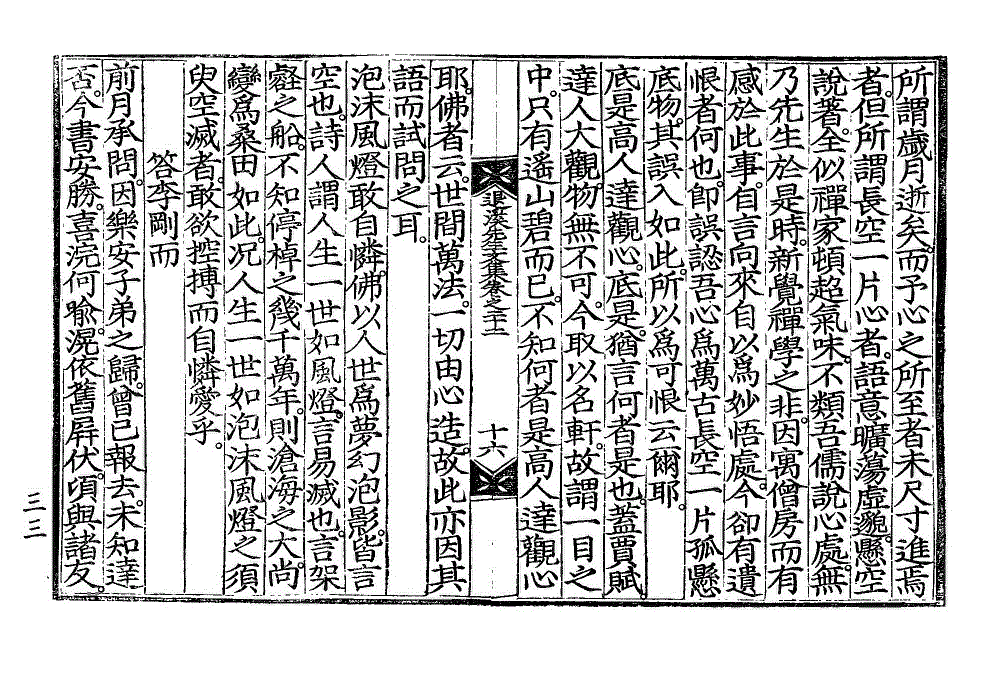 所谓岁月逝矣。而予心之所至者未尺寸进焉者。但所谓长空一片心者。语意旷荡虚邈。悬空说著。全似禅家顿超气味。不类吾儒说心处。无乃先生于是时。新觉禅学之非。因寓僧房而有感于此事。自言向来自以为妙悟处。今却有遗恨者何也。即误认吾心为万古长空一片孤悬底物。其误入如此。所以为可恨云尔耶。
所谓岁月逝矣。而予心之所至者未尺寸进焉者。但所谓长空一片心者。语意旷荡虚邈。悬空说著。全似禅家顿超气味。不类吾儒说心处。无乃先生于是时。新觉禅学之非。因寓僧房而有感于此事。自言向来自以为妙悟处。今却有遗恨者何也。即误认吾心为万古长空一片孤悬底物。其误入如此。所以为可恨云尔耶。底是高人达观心。底是。犹言何者是也。盖贾赋。达人大观。物无不可。今取以名轩。故谓一目之中。只有遥山碧而已。不知何者是高人达观心耶。佛者云。世间万法。一切由心造。故此亦因其语而试问之耳。
泡沫风灯敢自怜。佛以人世为梦幻泡影。皆言空也。诗人谓人生一世如风灯。言易灭也。言架壑之船。不知停棹之几千万年。则沧海之大。尚变为桑田如此。况人生一世如泡沫风灯之须臾空灭者。敢欲控搏而自怜爱乎。
答李刚而
前月承问。因乐安子弟之归。曾已报去。未知达否。今书安胜。喜浣何喻。滉依旧屏伏。顷与诸友。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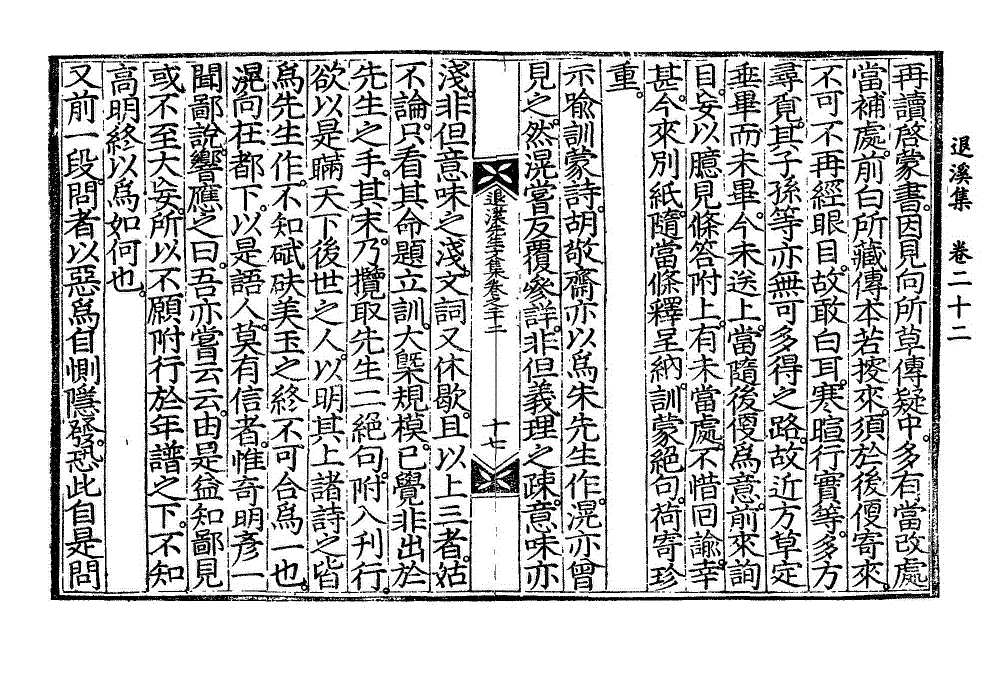 再读启蒙书。因见向所草传疑中。多有当改处当补处。前白所藏传本若搜来。须于后便寄来。不可不再经眼目。故敢白耳。寒暄行实等。多方寻觅。其子孙等亦无可多得之路。故近方草定垂毕而未毕。今未送上。当随后便为意。前来询目。妄以臆见条答附上。有未当处。不惜回谕。幸甚。今来别纸。随当条释呈纳。训蒙绝句。荷寄珍重。
再读启蒙书。因见向所草传疑中。多有当改处当补处。前白所藏传本若搜来。须于后便寄来。不可不再经眼目。故敢白耳。寒暄行实等。多方寻觅。其子孙等亦无可多得之路。故近方草定垂毕而未毕。今未送上。当随后便为意。前来询目。妄以臆见条答附上。有未当处。不惜回谕。幸甚。今来别纸。随当条释呈纳。训蒙绝句。荷寄珍重。示喻训蒙诗。胡敬斋亦以为朱先生作。滉亦曾见之。然滉尝反覆参详。非但义理之疏。意味亦浅。非但意味之浅。文词又休歇。且以上三者。姑不论。只看其命题立训。大槩规模。已觉非出于先生之手。其末。乃揽取先生二绝句。附入刊行。欲以是瞒天下后世之人。以明其上诸诗之皆为先生作。不知珷玞美玉之终不可合为一也。滉向在都下。以是语人。莫有信者。惟奇明彦一闻鄙说。响应之曰。吾亦尝云云。由是益知鄙见或不至大妄。所以不愿附行于年谱之下。不知高明终以为如何也。
又前一段。问者以恶为自恻隐发。恐此自是问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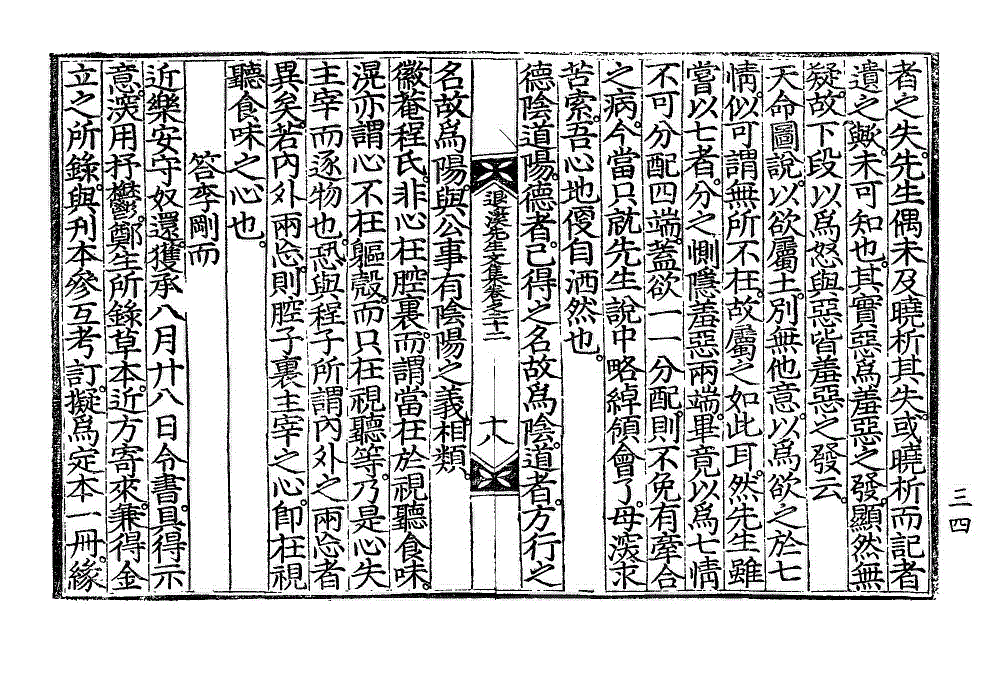 者之失。先生偶未及晓析其失。或晓析而记者遗之欤。未可知也。其实恶为羞恶之发。显然无疑。故下段以为怒与恶皆羞恶之发云。
者之失。先生偶未及晓析其失。或晓析而记者遗之欤。未可知也。其实恶为羞恶之发。显然无疑。故下段以为怒与恶皆羞恶之发云。天命图说。以欲属土。别无他意。以为欲之于七情。似可谓无所不在。故属之如此耳。然先生虽尝以七者。分之恻隐羞恶两端。毕竟以为七情不可分配四端。盖欲一一分配。则不免有牵合之病。今当只就先生说中略绰领会了。毋深求苦索。吾心地便自洒然也。
德阴道阳。德者。已得之名故为阴。道者。方行之名故为阳。与公事有阴阳之义。相类。
徽庵程氏。非心在腔里。而谓当在于视听食味。滉亦谓心不在躯壳。而只在视听等。乃是心失主宰而逐物也。恐与程子所谓内外之两忘者异矣。若内外两忘。则腔子里主宰之心。即在视听食味之心也。
答李刚而
近乐安守奴还。获承八月廿八日令书。具得示意。深用抒郁。郑生所录草本。近方寄来。兼得金立之所录。与刊本参互考订。拟为定本一册。缘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5H 页
 两人所录亦疏脱。莫由完备。然比之曾刊本。犹为彼善于此。不知如此。可绣梓以传否乎。其间。亦有滉所传闻录入者数三条。恐或非实。不可不质于其子孙。故寄示义兴。令其看审。若是实事非虚。则自彼直送于贵府。若非实而当改。则还之于此。容得改定而送之。以此谕于立之。未知立之如何处之耳。且寄示奇明彦所论与滉所见皆同。其中家范。令意以先生所自作为重。此意果然。滉当初意亦如此。已录全篇于卷中。反复详审。终觉未安处非一二。欲不录则意思甚好。可惜。录之则反有损于先生道德之高。不得已仿史家纪事传信不录其文之法。撮所为一条。录入卷中。然后始得见明彦之论及令喻之言。不能改定以从指教之意。亦不能尽同明彦之言。悚息悚息。令公亦曾见洪原所刊吉先生集否。其中所录山居序者。甚不满人意。恐或他人作。或少作。皆未可知。而刊入流传。甚未安。每恨当时收录者之不善计也。故今不敢效其所为。如何如何。凡其他去取僭妄之罪。粗见别册子。并望参照。有所不可。却以回喻。再三往复
两人所录亦疏脱。莫由完备。然比之曾刊本。犹为彼善于此。不知如此。可绣梓以传否乎。其间。亦有滉所传闻录入者数三条。恐或非实。不可不质于其子孙。故寄示义兴。令其看审。若是实事非虚。则自彼直送于贵府。若非实而当改。则还之于此。容得改定而送之。以此谕于立之。未知立之如何处之耳。且寄示奇明彦所论与滉所见皆同。其中家范。令意以先生所自作为重。此意果然。滉当初意亦如此。已录全篇于卷中。反复详审。终觉未安处非一二。欲不录则意思甚好。可惜。录之则反有损于先生道德之高。不得已仿史家纪事传信不录其文之法。撮所为一条。录入卷中。然后始得见明彦之论及令喻之言。不能改定以从指教之意。亦不能尽同明彦之言。悚息悚息。令公亦曾见洪原所刊吉先生集否。其中所录山居序者。甚不满人意。恐或他人作。或少作。皆未可知。而刊入流传。甚未安。每恨当时收录者之不善计也。故今不敢效其所为。如何如何。凡其他去取僭妄之罪。粗见别册子。并望参照。有所不可。却以回喻。再三往复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5L 页
 校覈。庶免大谬。而后入梓未晚也。来喻佔毕先生事。果然。其他亦多有如此之事。大抵于精一敬义之学。不甚留意。故驯致鹘突如此。可惜亦可惧也。鱼相世谦。闻其倜傥多奇节。亦 光庙朝出身。参翊戴功。他未有闻。馀未缕悉。
校覈。庶免大谬。而后入梓未晚也。来喻佔毕先生事。果然。其他亦多有如此之事。大抵于精一敬义之学。不甚留意。故驯致鹘突如此。可惜亦可惧也。鱼相世谦。闻其倜傥多奇节。亦 光庙朝出身。参翊戴功。他未有闻。馀未缕悉。别纸
寒暄公诗。滉亦有未晓处。然其大意谓此道至大。随时随处。无所不在。如裘葛然。君子出处之间。虽欲如霁行潦止之得宜。岂一一能中其节乎。(此二句已含讥讽意。言道不行而不能隐。失时中之义也。)使兰而苟得列乎众芳。则终当变芳香而化萧艾也必矣。夫牛可耕。马可乘。物各循性。谓之道。若兰变为萧。物不循性。如此则人何从而信此道之为道乎。(此讥责亦太露矣)
佔毕诗意。谓不幸而非分仕宦。忽至于卿大夫。其于匡救之事。行道之责。我何能任之。我之迂拙如此。后辈如君之嘲笑。固其宜也。然区区于乘势射利。以图进取之事。则吾亦不为之耳。官联。见周礼。言以官职相联。而同事王事也。
右两诗往复如此而已。秋江所谓佔毕,寒暄相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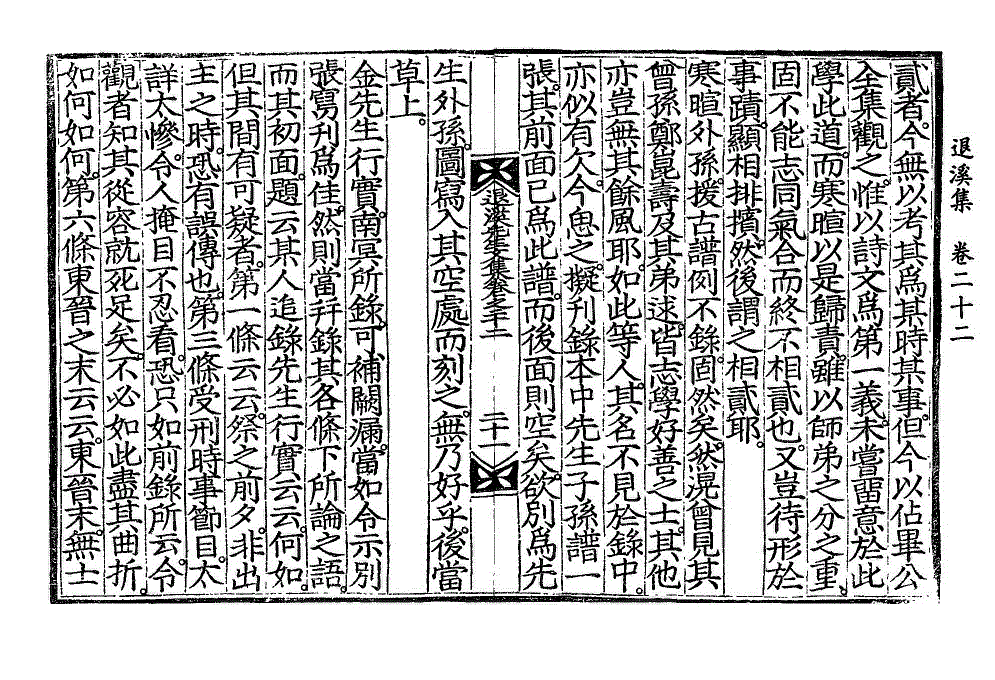 贰者。今无以考其为某时某事。但今以佔毕公全集观之。惟以诗文为第一义。未尝留意于此学此道。而寒暄以是归责。虽以师弟之分之重。固不能志同气合而终不相贰也。又岂待形于事迹。显相排摈。然后谓之相贰耶。
贰者。今无以考其为某时某事。但今以佔毕公全集观之。惟以诗文为第一义。未尝留意于此学此道。而寒暄以是归责。虽以师弟之分之重。固不能志同气合而终不相贰也。又岂待形于事迹。显相排摈。然后谓之相贰耶。寒暄外孙。援古谱例不录。固然矣。然滉曾见其曾孙郑昆寿及其弟逑。皆志学好善之士。其他亦岂无其馀风耶。如此等人。其名不见于录中。亦似有欠。今思之。拟刊录本中先生子孙谱一张。其前面已为此谱。而后面则空矣。欲别为先生外孙。图写入其空处而刻之。无乃好乎。后当草上。
金先生行实。南冥所录。可补阙漏。当如令示别张写刊为佳。然则当并录其各条下所论之语。而其初面。题云某人追录先生行实云云。何如。但其间有可疑者。第一条云云。祭之前夕。非出主之时。恐有误传也。第三条受刑时事节目。太详太惨。令人掩目不忍看。恐只如前录所云。令观者知其从容就死足矣。不必如此尽其曲折。如何如何。第六条东晋之末云云。东晋末。无士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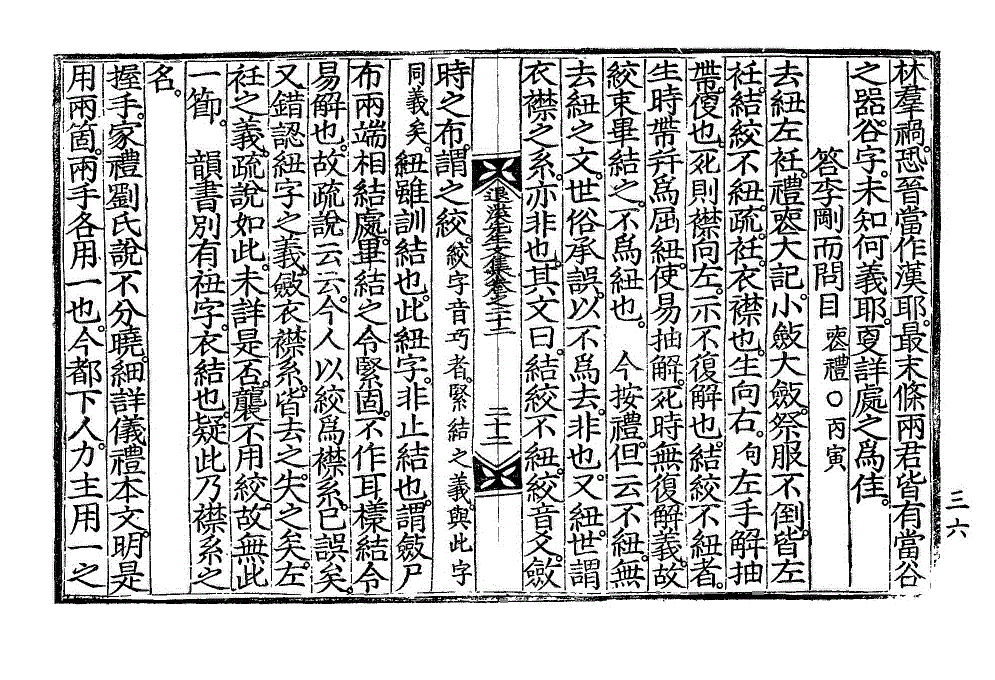 林群祸。恐晋当作汉耶。最末条两君皆有当谷之器。谷字。未知何义耶。更详处之为佳。
林群祸。恐晋当作汉耶。最末条两君皆有当谷之器。谷字。未知何义耶。更详处之为佳。答李刚而问目(丧礼○丙寅)
去纽左衽。礼丧大记。小敛大敛。祭服不倒。皆左衽。结绞不纽。疏。衽。衣襟也。生向右。(句)左手解抽带。便也。死则襟向左。示不复解也。结绞不纽者。生时带并为屈纽。使易抽解。死时无复解义。故绞束毕结之。不为纽也。 今按礼。但云不纽。无去纽之文。世俗承误。以不为去。非也。又纽。世谓衣襟之系。亦非也。其文曰。结绞不纽。绞音爻。敛时之布。谓之绞。(绞字音巧者。紧结之义。与此字同义矣。)纽虽训结也。此纽字。非止结也。谓敛尸布两端相结处。毕结之令紧固。不作耳样结令易解也。故疏说云云。今人以绞为襟系。已误矣。又错认纽字之义。敛衣襟系。皆去之。失之矣。左衽之义。疏说如此。未详是否。袭不用绞。故无此一节。 韵书别有𧘥字。衣结也。疑此乃襟系之名。
握手。家礼刘氏说不分晓。细详仪礼本文。明是用两个。两手各用一也。今都下人。力主用一之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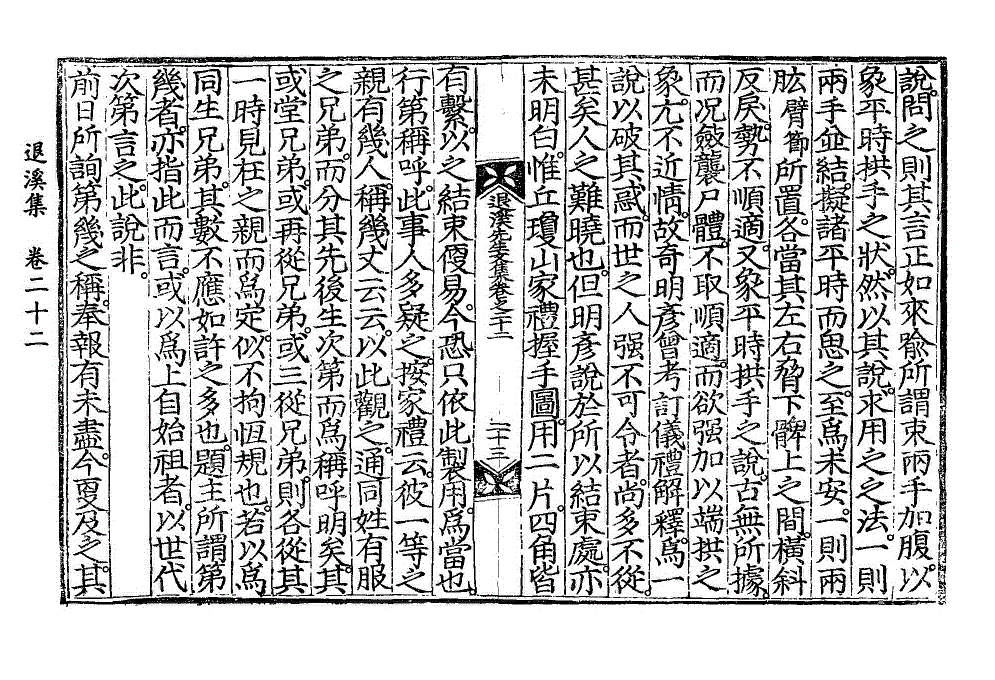 说。问之则其言正如来喻所谓束两手加腹。以象平时拱手之状。然以其说。求用之之法。一则两手并结。拟诸平时而思之。至为未安。一则两肱(臂节)所置。各当其左右胁下髀上之间。横斜反戾。势不顺适。又象平时拱手之说。古无所据。而况敛袭尸体。不取顺适。而欲强加以端拱之象。尤不近情。故奇明彦曾考订仪礼解释。为一说以破其惑。而世之人强不可令者。尚多不从。甚矣人之难晓也。但明彦说于所以结束处。亦未明白。惟丘琼山家礼握手图。用二片。四角皆有系。以之结束便易。今恐只依此制用。为当也。行第称呼。此事人多疑之。按家礼云。彼一等之亲有几人。称几丈云云。以此观之。通同姓有服之兄弟。而分其先后生次第而为称呼明矣。其或堂兄弟。或再从兄弟。或三从兄弟。则各从其一时见在之亲而为定。似不拘恒规也。若以为同生兄弟。其数不应如许之多也。题主所谓第几者。亦指此而言。或以为上自始祖者。以世代次第言之。此说非。
说。问之则其言正如来喻所谓束两手加腹。以象平时拱手之状。然以其说。求用之之法。一则两手并结。拟诸平时而思之。至为未安。一则两肱(臂节)所置。各当其左右胁下髀上之间。横斜反戾。势不顺适。又象平时拱手之说。古无所据。而况敛袭尸体。不取顺适。而欲强加以端拱之象。尤不近情。故奇明彦曾考订仪礼解释。为一说以破其惑。而世之人强不可令者。尚多不从。甚矣人之难晓也。但明彦说于所以结束处。亦未明白。惟丘琼山家礼握手图。用二片。四角皆有系。以之结束便易。今恐只依此制用。为当也。行第称呼。此事人多疑之。按家礼云。彼一等之亲有几人。称几丈云云。以此观之。通同姓有服之兄弟。而分其先后生次第而为称呼明矣。其或堂兄弟。或再从兄弟。或三从兄弟。则各从其一时见在之亲而为定。似不拘恒规也。若以为同生兄弟。其数不应如许之多也。题主所谓第几者。亦指此而言。或以为上自始祖者。以世代次第言之。此说非。前日所询第几之称。奉报有未尽。今更及之。其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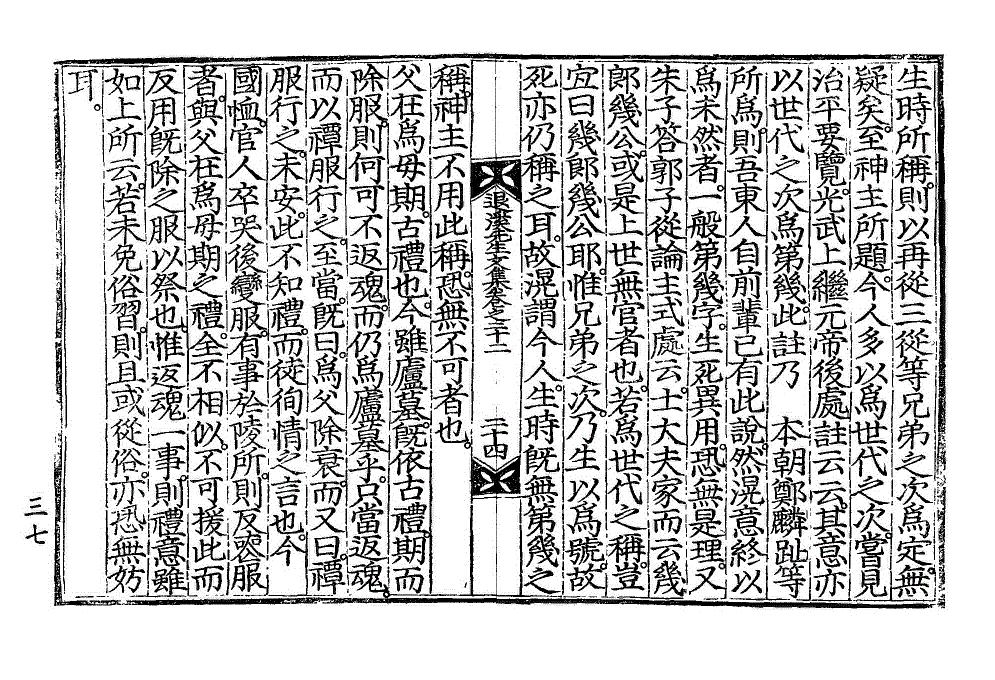 生时所称。则以再从三从等兄弟之次为定。无疑矣。至神主所题。今人多以为世代之次。尝见治平要览。光武上继元帝后处注云云。其意亦以世代之次为第几。此注乃 本朝郑麟趾等所为。则吾东人自前辈已有此说。然滉意终以为未然者。一般第几字。生死异用。恐无是理。又朱子答郭子从论主式处云。士大夫家而云几郎几公。或是上世无官者也。若为世代之称。岂宜曰几郎几公耶。惟兄弟之次。乃生以为号。故死亦仍称之耳。故滉谓今人。生时既无第几之称。神主不用此称。恐无不可者也。
生时所称。则以再从三从等兄弟之次为定。无疑矣。至神主所题。今人多以为世代之次。尝见治平要览。光武上继元帝后处注云云。其意亦以世代之次为第几。此注乃 本朝郑麟趾等所为。则吾东人自前辈已有此说。然滉意终以为未然者。一般第几字。生死异用。恐无是理。又朱子答郭子从论主式处云。士大夫家而云几郎几公。或是上世无官者也。若为世代之称。岂宜曰几郎几公耶。惟兄弟之次。乃生以为号。故死亦仍称之耳。故滉谓今人。生时既无第几之称。神主不用此称。恐无不可者也。父在为母期。古礼也。今虽庐墓。既依古礼。期而除服。则何可不返魂。而仍为庐墓乎。只当返魂。而以禫服行之。至当。既曰。为父除衰。而又曰。禫服行之。未安。此不知礼。而徒徇情之言也。今 国恤。官人卒哭后变服。有事于陵所。则反丧服者。与父在为母期之礼。全不相似。不可援此而反用既除之服以祭也。惟返魂一事。则礼意虽如上所云。若未免俗习。则且或从俗。亦恐无妨耳。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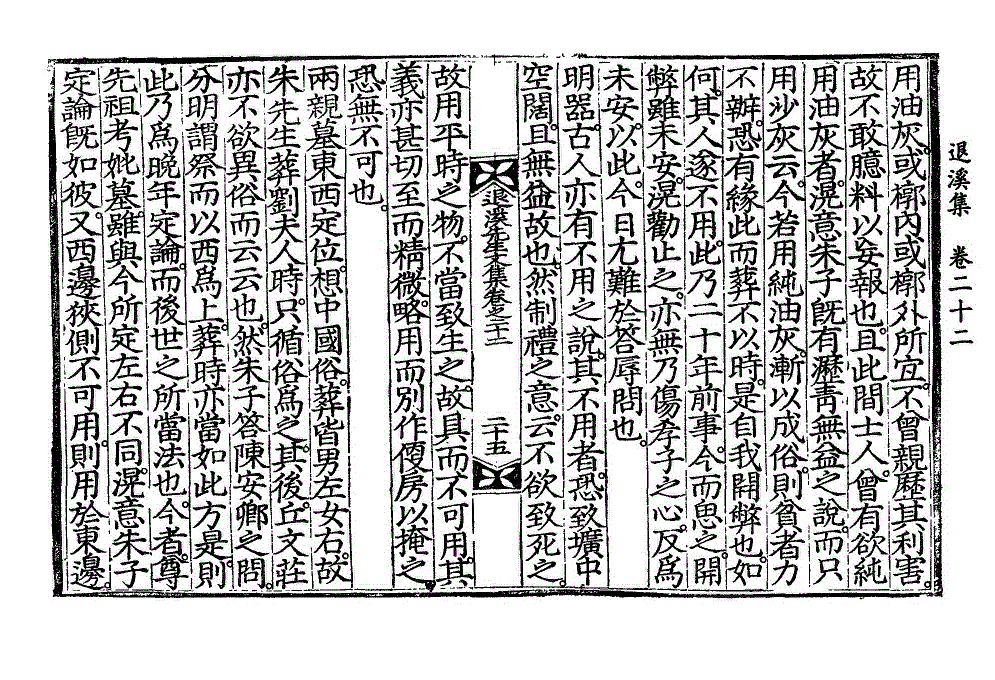 用油灰。或椁内或椁外所宜。不曾亲历其利害。故不敢臆料以妄报也。且此间士人。曾有欲纯用油灰者。滉意朱子既有沥青无益之说。而只用沙灰云。今若用纯油灰。渐以成俗。则贫者力不办。恐有缘此而葬不以时。是自我开弊也。如何。其人遂不用。此乃二十年前事。今而思之。开弊虽未安。滉劝止之。亦无乃伤孝子之心。反为未安。以此。今日尤难于答辱问也。
用油灰。或椁内或椁外所宜。不曾亲历其利害。故不敢臆料以妄报也。且此间士人。曾有欲纯用油灰者。滉意朱子既有沥青无益之说。而只用沙灰云。今若用纯油灰。渐以成俗。则贫者力不办。恐有缘此而葬不以时。是自我开弊也。如何。其人遂不用。此乃二十年前事。今而思之。开弊虽未安。滉劝止之。亦无乃伤孝子之心。反为未安。以此。今日尤难于答辱问也。明器。古人亦有不用之说。其不用者。恐致圹中空阔。且无益故也。然制礼之意。云不欲致死之。故用平时之物。不当致生之。故具而不可用。其义亦甚切至而精微。略用而别作便房以掩之。恐无不可也。
两亲墓东西定位。想中国俗。葬皆男左女右。故朱先生葬刘夫人时。只循俗为之。其后。丘文庄亦不欲异俗而云云也。然朱子答陈安卿之问。分明谓祭而以西为上。葬时亦当如此方是。则此乃为晚年定论。而后世之所当法也。今者。尊先祖考妣墓。虽与今所定左右不同。滉意朱子定论既如彼。又西边狭侧不可用。则用于东边。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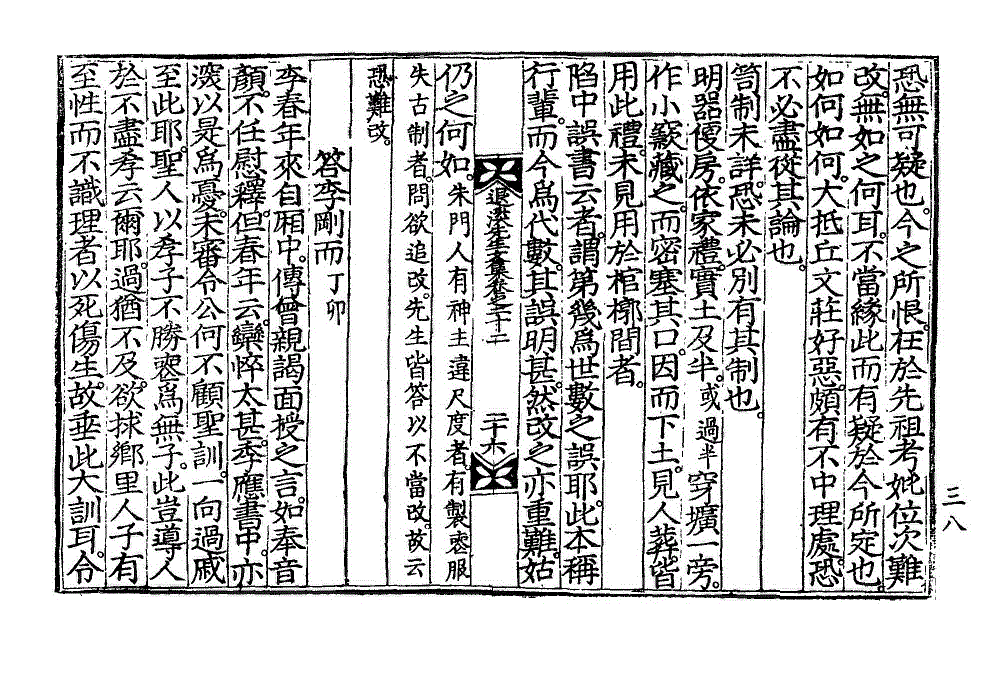 恐无可疑也。今之所恨。在于先祖考妣位次难改。无如之何耳。不当缘此而有疑于今所定也。如何如何。大抵丘文庄好恶。颇有不中理处。恐不必尽从其论也。
恐无可疑也。今之所恨。在于先祖考妣位次难改。无如之何耳。不当缘此而有疑于今所定也。如何如何。大抵丘文庄好恶。颇有不中理处。恐不必尽从其论也。笥制未详。恐未必别有其制也。
明器便房。依家礼。实土及半。(或过半)穿圹一旁。作小窾藏之。而密塞其口。因而下土。见人葬。皆用此礼。未见用于棺椁间者。
陷中误书云者。谓第几为世数之误耶。此本称行辈。而今为代数。其误明甚。然改之亦重难。姑仍之何如。(朱门人有神主违尺度者。有制丧服失古制者。问欲追改。先生皆答以不当改。故云恐难改。)
答李刚而(丁卯)
李春年来自厢中。传曾亲谒面授之言。如奉音颜。不任慰释。但春年云。栾悴太甚。季应书中。亦深以是为忧。未审令公何不顾圣训。一向过戚至此耶。圣人以孝子不胜丧为无子。此岂导人于不尽孝云尔耶。过犹不及。欲救乡里人子有至性而不识理者以死伤生。故垂此大训耳。令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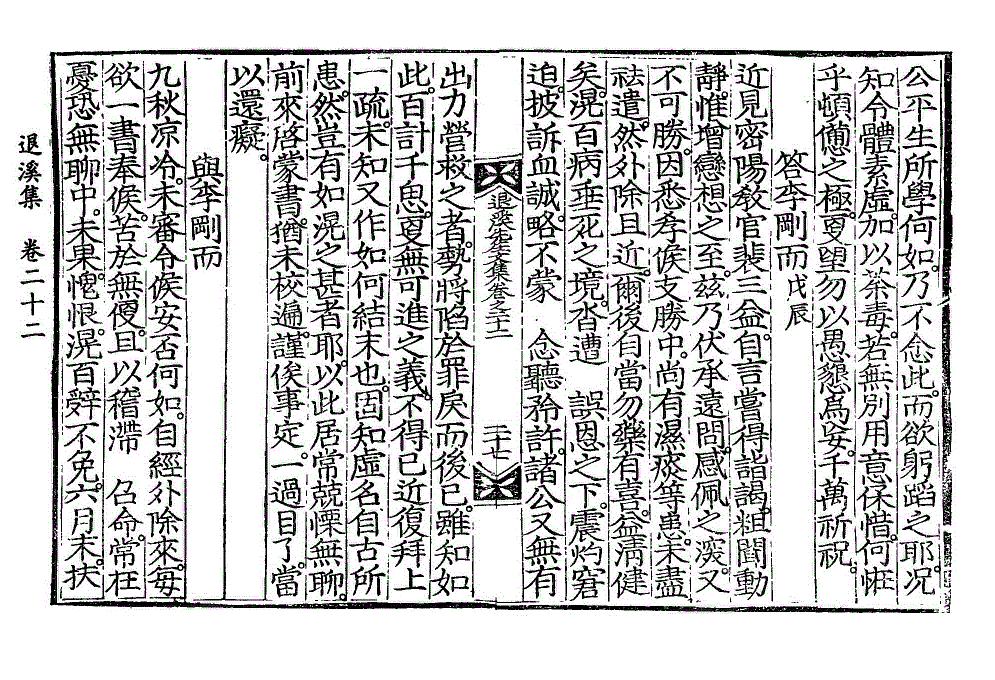 公平生所学何如。乃不念此。而欲躬蹈之耶。况知令体素虚。加以荼毒。若无别用意保惜。何怪乎顿惫之极。更望勿以愚恳为妄。千万祈祝。
公平生所学何如。乃不念此。而欲躬蹈之耶。况知令体素虚。加以荼毒。若无别用意保惜。何怪乎顿惫之极。更望勿以愚恳为妄。千万祈祝。答李刚而(戊辰)
近见密阳教官裴三益。自言尝得诣谒。粗闻动静。惟增恋想之至。玆乃伏承远问。感佩之深。又不可胜。因悉孝候支胜中。尚有湿痰等患。未尽祛遣。然外除且近。尔后自当勿药有喜。益清健矣。滉百病垂死之境。沓遭 误恩之下。震灼窘迫。披诉血诚。略不蒙 念听矜许。诸公又无有出力营救之者。势将陷于罪戾而后已。虽知如此。百计千思。更无可进之义。不得已近复拜上一疏。未知又作如何结末也。固知虚名自古所患。然岂有如滉之甚者耶。以此居常兢慄无聊。前来启蒙书。犹未校遍。谨俟事定。一过目了。当以还痴。
与李刚而
九秋凉冷。未审令候安否何如。自经外除来。每欲一书奉候。苦于无便。且以稽滞 召命。常在忧恐无聊中。未果。愧恨。滉百辞不免。六月末。扶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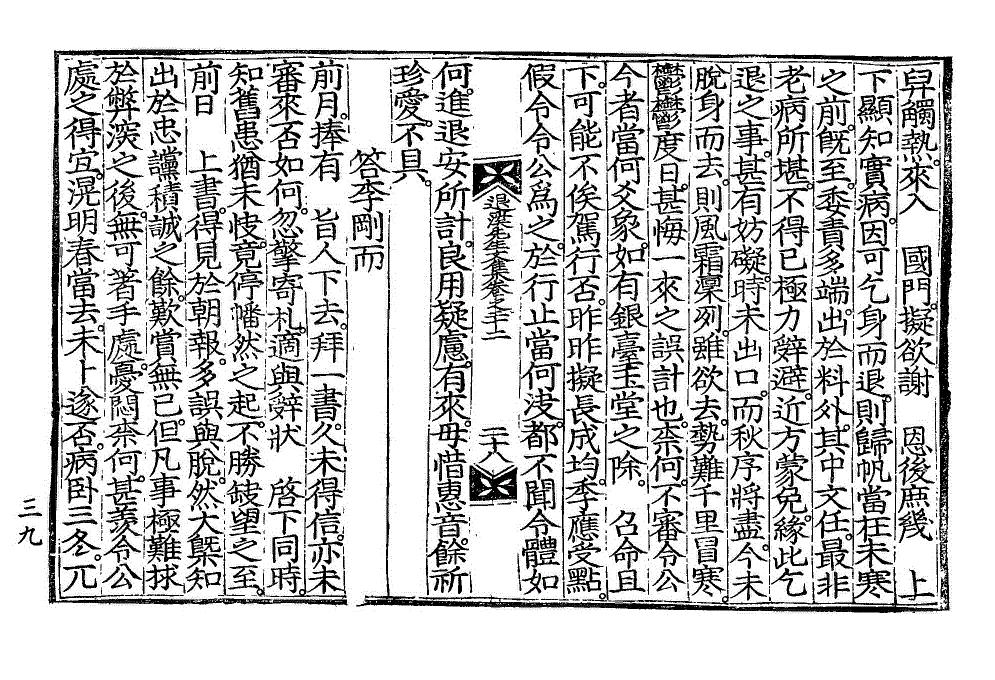 舁触热。来入 国门。拟欲谢 恩后庶几 上下显知实病。因可乞身而退。则归帆当在未寒之前。既至。委责多端。出于料外。其中文任。最非老病所堪。不得已极力辞避。近方蒙免。缘此乞退之事。甚有妨碍。时未出口。而秋序将尽。今未脱身而去。则风霜凛冽。虽欲去。势难千里冒寒。郁郁度日。甚悔一来之误计也。柰何。不审令公今者当何爻象。如有银台,玉堂之除。 召命且下。可能不俟驾行否。昨昨拟长成均。季应受点。假令令公为之。于行止当何决。都不闻令体如何。进退安所计。良用疑虑。有来。毋惜惠音。馀祈珍爱。不具。
舁触热。来入 国门。拟欲谢 恩后庶几 上下显知实病。因可乞身而退。则归帆当在未寒之前。既至。委责多端。出于料外。其中文任。最非老病所堪。不得已极力辞避。近方蒙免。缘此乞退之事。甚有妨碍。时未出口。而秋序将尽。今未脱身而去。则风霜凛冽。虽欲去。势难千里冒寒。郁郁度日。甚悔一来之误计也。柰何。不审令公今者当何爻象。如有银台,玉堂之除。 召命且下。可能不俟驾行否。昨昨拟长成均。季应受点。假令令公为之。于行止当何决。都不闻令体如何。进退安所计。良用疑虑。有来。毋惜惠音。馀祈珍爱。不具。答李刚而
前月。捧有 旨人下去。拜一书。久未得信。亦未审来否如何。忽擎寄札。适与辞状 启下同时。知旧患犹未快。竟停幡然之起。不胜缺望之至。前日 上书。得见于朝报。多误与脱。然大槩知出于忠谠积诚之馀。叹赏无已。但凡事极难救于弊深之后。无可著手处。忧闷柰何。甚羡令公处之得宜。滉明春当去。未卜遂否。病卧三冬。兀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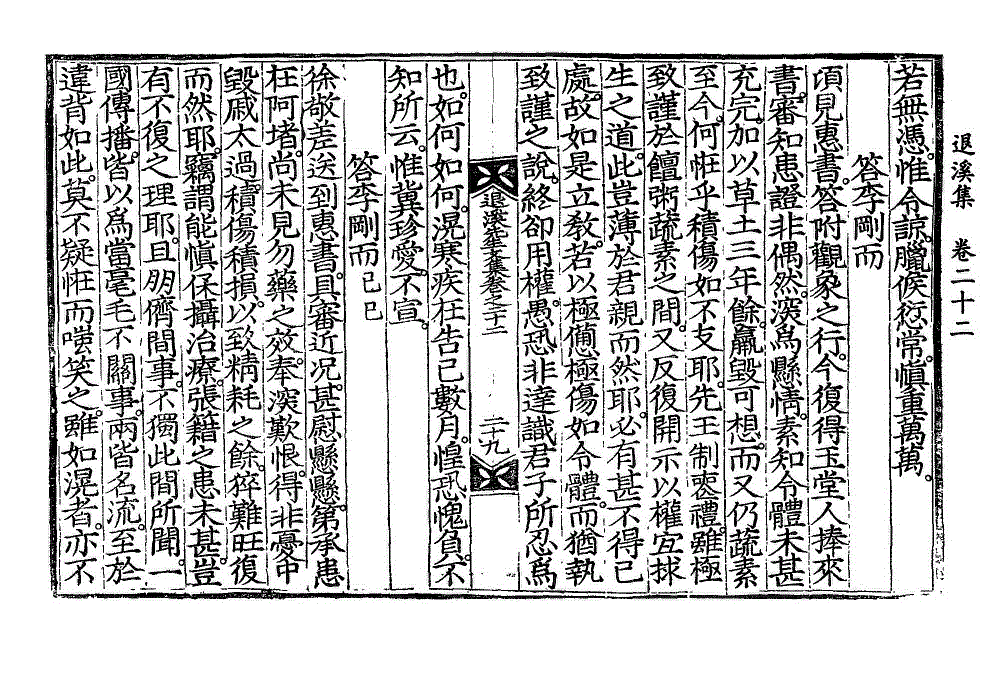 若无凭。惟令谅。腊候愆常。慎重万万。
若无凭。惟令谅。腊候愆常。慎重万万。答李刚而
顷见惠书。答附观象之行。今复得玉堂人捧来书。审知患證非偶然。深为悬情。素知令体未甚充完。加以草土三年馀。羸毁可想。而又仍蔬素至今。何怪乎积伤如不支耶。先王制丧礼。虽极致谨于饘粥蔬素之间。又反复开示以权宜救生之道。此岂薄于君亲而然耶。必有甚不得已处。故如是立教。若以极惫极伤如令体。而犹执致谨之说。终却用权。愚恐非达识君子所忍为也。如何如何。滉寒疾在告已数月。惶恐愧负。不知所云。惟冀珍爱。不宣。
答李刚而(己巳)
徐敬差送到惠书。具审近况。甚慰悬悬。第承患在阿堵。尚未见勿药之效。奉深叹恨。得非忧中毁戚太过。积伤积损。以致精耗之馀。猝难旺复而然耶。窃谓能慎保摄治疗。张籍之患未甚。岂有不复之理耶。且朋侪间事。不独此间所闻。一国传播。皆以为当毫毛不关事。两皆名流。至于违背如此。莫不疑怪而嗤笑之。虽如滉者。亦不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40L 页
 免为两君嗟惜之深。传疑书。即当回纳。但与此间诸人所传录者相混。未能分辨。他日在京儿孙下来。辨出后寄纳。伏惟照谅。
免为两君嗟惜之深。传疑书。即当回纳。但与此间诸人所传录者相混。未能分辨。他日在京儿孙下来。辨出后寄纳。伏惟照谅。答李刚而(庚午)
雁僧又来。承睹惠书。兼之问僧。颇得起居之详。积郁雾披。但寻常远想。免丧以来。往年所苦。自应豁除。日向清茂矣。今示诸患尚尔非一。重以山行失护。致有损伤。乃至经时越岁。少见安日。为左右深觉悬悬也。去春半。宜宁奴来还。拜一书附送。令其即时往呈。如或答书。俟便寄来。岂谓至今不传。奴顽甚矣。别纸数事。各有草报。幸可笑领。所谓意外之患者。亦于别纸略及之。大槩愚意。不欲令公惮其言而力为发明。又不须屈己求合也。滉去年之退。已无复入之理。加以七十之年。适当此际。请遂至愿。可谓天幸之会。圣德如天。本无还 召之意。缘诸公枉费拈挑。复此缠拘。深讶诸公不为人开一好径路也。去五月。得 圣旨有调来之语。赖此偷假时月之间。然终非所安。将复冒渎上请。笺已草定。窃闻朝廷方有论请。殊未安靖。姑且停候。日夕兢慄。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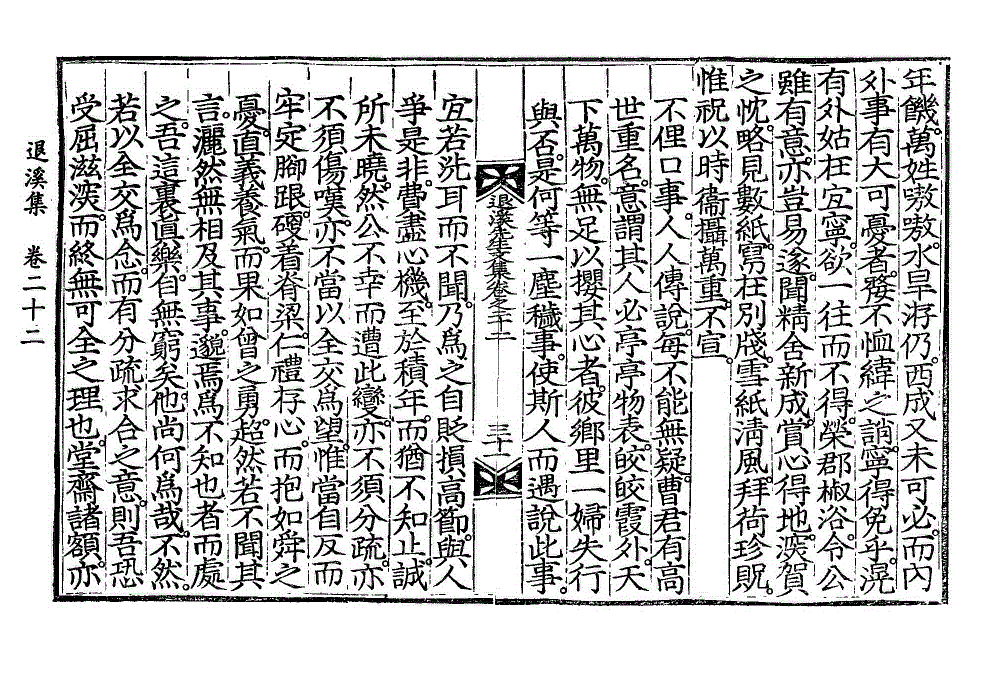 年饥。万姓嗷嗷。水旱荐仍。西成又未可必。而内外事有大可忧者。嫠不恤纬之诮。宁得免乎。滉有外姑在宜宁。欲一往而不得。荣郡椒浴。令公虽有意。亦岂易遂。闻精舍新成。赏心得地。深贺之忱。略见数纸。写在别笺。雪纸清风。拜荷珍贶。惟祝以时卫摄万重。不宣。
年饥。万姓嗷嗷。水旱荐仍。西成又未可必。而内外事有大可忧者。嫠不恤纬之诮。宁得免乎。滉有外姑在宜宁。欲一往而不得。荣郡椒浴。令公虽有意。亦岂易遂。闻精舍新成。赏心得地。深贺之忱。略见数纸。写在别笺。雪纸清风。拜荷珍贶。惟祝以时卫摄万重。不宣。不俚口事。人人传说。每不能无疑。曹君有高世重名。意谓其人必亭亭物表。皎皎霞外。天下万物。无足以撄其心者。彼乡里一妇失行与否。是何等一尘秽事。使斯人而遇说此事。宜若洗耳而不闻。乃为之自贬损高节。与人争是非。费尽心机。至于积年。而犹不知止。诚所未晓。然公不幸而遭此变。亦不须分疏。亦不须伤叹。亦不当以全交为望。惟当自反而牢定脚跟。硬着脊梁。仁礼存心。而抱如舜之忧。直义养气。而果如曾之勇。超然若不闻其言。洒然无相及其事。邈焉为不知也者而处之。吾这里真乐。自无穷矣。他尚何为哉。不然。若以全交为念。而有分疏求合之意。则吾恐受屈滋深。而终无可全之理也。堂斋诸额。亦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第 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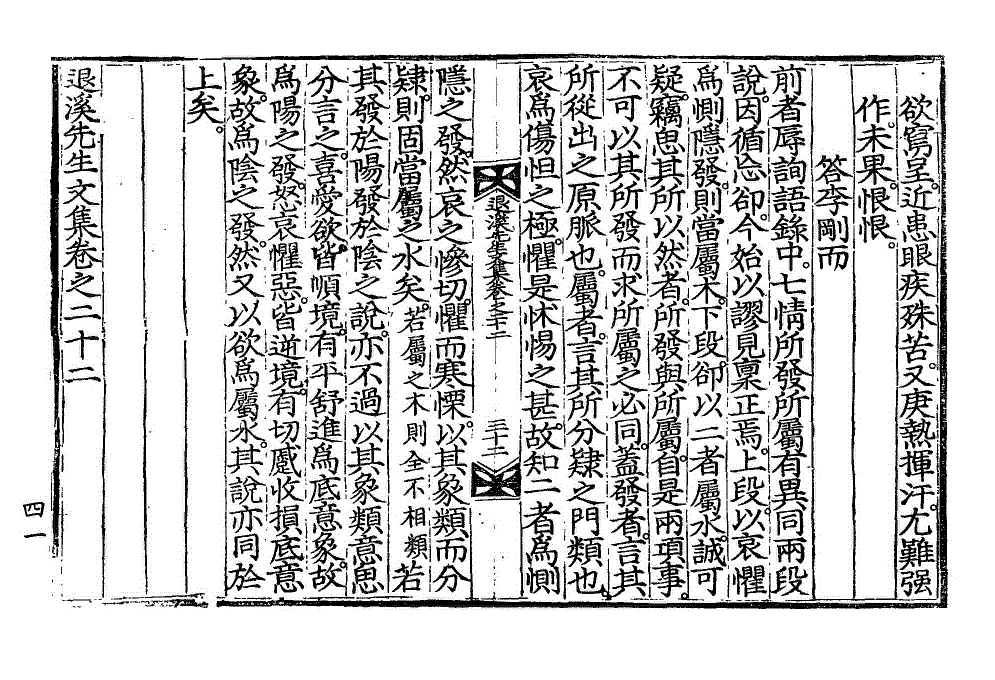 欲写呈。近患眼疾殊苦。又庚热挥汗。尤难强作。未果。恨恨。
欲写呈。近患眼疾殊苦。又庚热挥汗。尤难强作。未果。恨恨。答李刚而
前者辱询语录中。七情所发所属有异同两段说。因循忘却。今始以谬见禀正焉。上段。以哀惧为恻隐发。则当属木。下段。却以二者属水。诚可疑。窃思其所以然者。所发与所属。自是两项事。不可以其所发而求所属之必同。盖发者。言其所从出之原脉也。属者。言其所分肄之门类也。哀为伤怛之极。惧是怵惕之甚。故知二者为恻隐之发。然哀之惨切。惧而寒慄。以其象类而分肄。则固当属之水矣。(若属之木则全不相类)若其发于阳发于阴之说。亦不过以其象类意思分言之。喜爱欲。皆顺境。有平舒进为底意象。故为阳之发。怒哀惧恶。皆逆境。有切蹙收损底意象。故为阴之发。然又以欲为属水。其说亦同于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