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晦斋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x 页
晦斋先生集卷之十二
[拾遗]○疏
[拾遗]○疏
晦斋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4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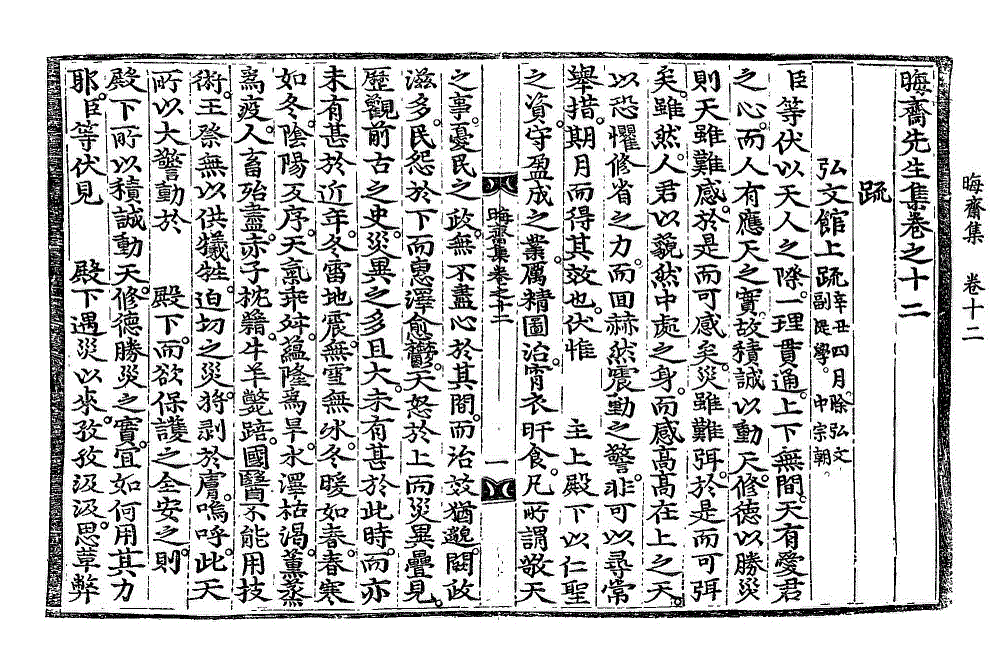 弘文馆上疏(辛丑四月。除弘文副提学。 中宗朝。)
弘文馆上疏(辛丑四月。除弘文副提学。 中宗朝。)臣等伏以天人之际。一理贯通。上下无间。天有爱君之心。而人有应天之实。故积诚以动天。修德以胜灾则天虽难感。于是而可感矣。灾虽难弭。于是而可弭矣。虽然。人君以藐然中处之身。而感高高在上之天。以恐惧修省之力。而回赫然震动之警。非可以寻常举措。期月而得其效也。伏惟 主上殿下以仁圣之资。守盈成之业。厉精图治。宵衣旰食。凡所谓敬天之事。忧民之政。无不尽心于其间。而治效犹邈。阙政滋多。民怨于下而惠泽愈郁。天怒于上而灾异叠见。历观前古之史。灾异之多且大。未有甚于此时。而亦未有甚于近年。冬雷地震。无雪无冰。冬暖如春。春寒如冬。阴阳反序。天气乖舛。蕴隆为旱。水泽枯渴。薰蒸为疫。人畜殆尽。赤子枕藉。牛羊毙踣。国医不能用技术。王祭无以供牺牲。迫切之灾。将剥于肤。呜呼。此天所以大警动于 殿下。而欲保护之全安之。则 殿下所以积诚动天。修德胜灾之实。宜如何用其力耶。臣等伏见 殿下遇灾以来。孜孜汲汲。思革弊
晦斋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4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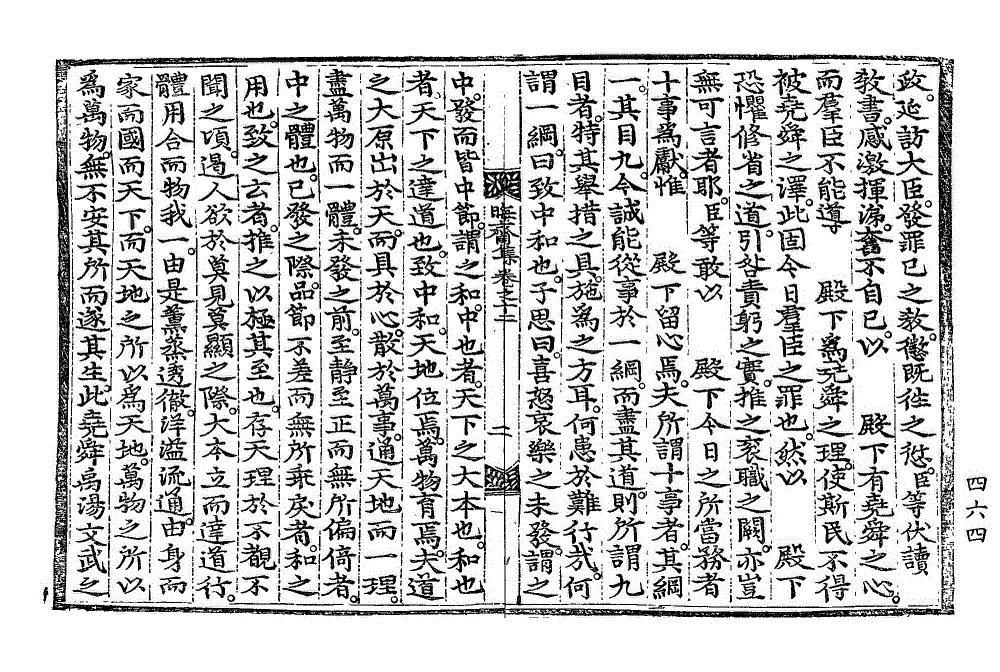 政。延访大臣。发罪己之教。惩既往之愆。臣等伏读 教书。感激挥涕。奋不自已。以 殿下有尧舜之心。而群臣不能导 殿下为尧舜之理。使斯民不得被尧舜之泽。此固今日群臣之罪也。然以 殿下恐惧修省之道。引咎责躬之实。推之衮职之阙。亦岂无可言者耶。臣等敢以 殿下今日之所当务者十事为献。惟 殿下留心焉。夫所谓十事者。其纲一。其目九。今诚能从事于一纲。而尽其道。则所谓九目者。特其举措之具。施为之方耳。何患于难行哉。何谓一纲。曰致中和也。子思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夫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具于心。散于万事。通天地而一理。尽万物而一体。未发之前。至静至正而无所偏倚者。中之体也。已发之际。品节不差而无所乖戾者。和之用也。致之云者。推之以极其至也。存天理于不睹不闻之顷。遏人欲于莫见莫显之际。大本立而达道行。体用合而物我一。由是薰蒸透彻。洋溢流通。由身而家而国而天下。而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万物之所以为万物。无不安其所而遂其生。此尧舜禹汤文武之
政。延访大臣。发罪己之教。惩既往之愆。臣等伏读 教书。感激挥涕。奋不自已。以 殿下有尧舜之心。而群臣不能导 殿下为尧舜之理。使斯民不得被尧舜之泽。此固今日群臣之罪也。然以 殿下恐惧修省之道。引咎责躬之实。推之衮职之阙。亦岂无可言者耶。臣等敢以 殿下今日之所当务者十事为献。惟 殿下留心焉。夫所谓十事者。其纲一。其目九。今诚能从事于一纲。而尽其道。则所谓九目者。特其举措之具。施为之方耳。何患于难行哉。何谓一纲。曰致中和也。子思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夫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具于心。散于万事。通天地而一理。尽万物而一体。未发之前。至静至正而无所偏倚者。中之体也。已发之际。品节不差而无所乖戾者。和之用也。致之云者。推之以极其至也。存天理于不睹不闻之顷。遏人欲于莫见莫显之际。大本立而达道行。体用合而物我一。由是薰蒸透彻。洋溢流通。由身而家而国而天下。而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万物之所以为万物。无不安其所而遂其生。此尧舜禹汤文武之晦斋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465H 页
 君所以参天地赞化育。俯仰无愧。麒麟游其薮。凤凰鸣于冈。而无妖孽灾变之作也。夫以 殿下之明。而犹有今日之忧者。无他。 圣学之功有未尽。而中和之致有未极也。进言者有曰。 圣学既已高明矣。若无复屑意于问学而可者。噫。为是言者。惟知以经史间涉猎之功赞 殿下之学。而不以尧舜三王之道望于 殿下也。惟古之圣帝明王。知道之无时不然。故无一时而非学。知道之无物不有。故无一事而非学。以至盘盂有铭。几杖有戒。亵御之箴。瞽史之讽。凡所以操存此心。培养德性者。无所不用其至矣。今也无此数事。惟贤士大夫之得近清光。讲论规戒者。自 经筵数刻之外无闻。而进讲之书。又非二帝三王授受心法之旨。孔孟程朱传道讲学之要。则 圣学之得于 经筵者。恐未足以日进乎高明之域矣。自此之外。深居 九重之内。左右燕闲之侍。惟宦官宫妾之辈。无芝兰俱化之益。有一曝十寒之惧则当此之时。 圣学之所以用功者。臣等未得而知之也。窃恐渊蜎蠖濩之中。虚明应物之地。存养省察之功有所未至。而大本之立未能坚确。故达道之行。多所壅阏。由是。宫禁不得有所闲而严。纪
君所以参天地赞化育。俯仰无愧。麒麟游其薮。凤凰鸣于冈。而无妖孽灾变之作也。夫以 殿下之明。而犹有今日之忧者。无他。 圣学之功有未尽。而中和之致有未极也。进言者有曰。 圣学既已高明矣。若无复屑意于问学而可者。噫。为是言者。惟知以经史间涉猎之功赞 殿下之学。而不以尧舜三王之道望于 殿下也。惟古之圣帝明王。知道之无时不然。故无一时而非学。知道之无物不有。故无一事而非学。以至盘盂有铭。几杖有戒。亵御之箴。瞽史之讽。凡所以操存此心。培养德性者。无所不用其至矣。今也无此数事。惟贤士大夫之得近清光。讲论规戒者。自 经筵数刻之外无闻。而进讲之书。又非二帝三王授受心法之旨。孔孟程朱传道讲学之要。则 圣学之得于 经筵者。恐未足以日进乎高明之域矣。自此之外。深居 九重之内。左右燕闲之侍。惟宦官宫妾之辈。无芝兰俱化之益。有一曝十寒之惧则当此之时。 圣学之所以用功者。臣等未得而知之也。窃恐渊蜎蠖濩之中。虚明应物之地。存养省察之功有所未至。而大本之立未能坚确。故达道之行。多所壅阏。由是。宫禁不得有所闲而严。纪晦斋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4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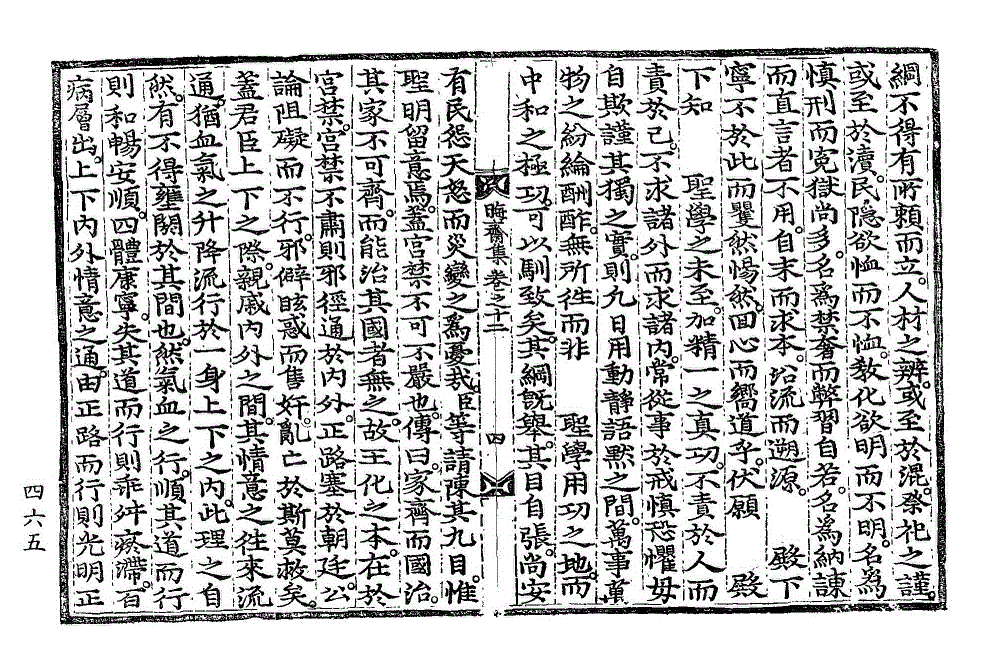 纲不得有所赖而立。人材之辨。或至于混。祭祀之谨。或至于渎。民隐欲恤而不恤。教化欲明而不明。名为慎刑而冤狱尚多。名为禁奢而弊习自若。名为纳谏而直言者不用。自末而求本。沿流而溯源。 殿下宁不于此而矍然惕然。回心而向道乎。伏愿 殿下知 圣学之未至。加精一之真功。不责于人而责于己。不求诸外而求诸内。常从事于戒慎恐惧毋自欺谨其独之实。则凡日用动静语默之间。万事万物之纷纶酬酢。无所往而非 圣学用功之地。而中和之极功。可以驯致矣。其纲既举。其目自张。尚安有民怨天怒而灾变之为忧哉。臣等请陈其九目。惟圣明留意焉。盖宫禁不可不严也。传曰。家齐而国治。其家不可齐。而能治其国者无之。故王化之本。在于宫禁。宫禁不肃则邪径通于内外。正路塞于朝廷。公论阻碍而不行。邪僻眩惑而售奸。乱亡于斯莫救矣。盖君臣上下之际。亲戚内外之间。其情意之往来流通。犹血气之升降流行于一身上下之内。此理之自然。有不得壅阏于其间也。然气血之行。顺其道而行则和畅安顺。四体康宁。失其道而行则乖舛瘀滞。百病层出。上下内外情意之通。由正路而行则光明正
纲不得有所赖而立。人材之辨。或至于混。祭祀之谨。或至于渎。民隐欲恤而不恤。教化欲明而不明。名为慎刑而冤狱尚多。名为禁奢而弊习自若。名为纳谏而直言者不用。自末而求本。沿流而溯源。 殿下宁不于此而矍然惕然。回心而向道乎。伏愿 殿下知 圣学之未至。加精一之真功。不责于人而责于己。不求诸外而求诸内。常从事于戒慎恐惧毋自欺谨其独之实。则凡日用动静语默之间。万事万物之纷纶酬酢。无所往而非 圣学用功之地。而中和之极功。可以驯致矣。其纲既举。其目自张。尚安有民怨天怒而灾变之为忧哉。臣等请陈其九目。惟圣明留意焉。盖宫禁不可不严也。传曰。家齐而国治。其家不可齐。而能治其国者无之。故王化之本。在于宫禁。宫禁不肃则邪径通于内外。正路塞于朝廷。公论阻碍而不行。邪僻眩惑而售奸。乱亡于斯莫救矣。盖君臣上下之际。亲戚内外之间。其情意之往来流通。犹血气之升降流行于一身上下之内。此理之自然。有不得壅阏于其间也。然气血之行。顺其道而行则和畅安顺。四体康宁。失其道而行则乖舛瘀滞。百病层出。上下内外情意之通。由正路而行则光明正晦斋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4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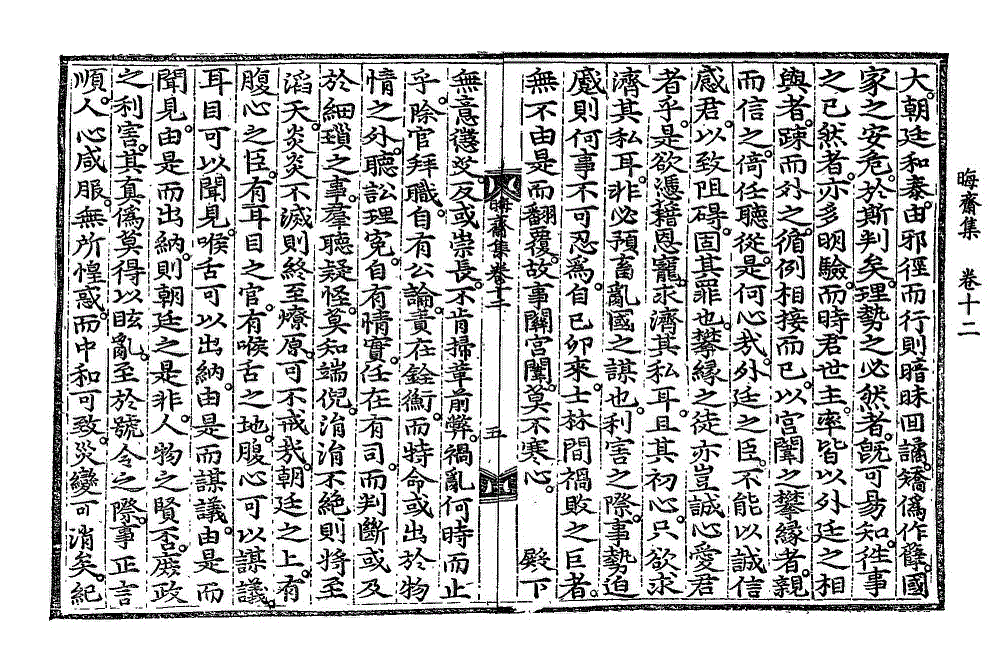 大。朝廷和泰。由邪径而行则暗昧回谲。矫伪作孽。国家之安危。于斯判矣。理势之必然者。既可易知。往事之已然者。亦多明验。而时君世主。率皆以外廷之相与者。疏而外之。循例相接而已。以宫闱之攀缘者。亲而信之。倚任听从。是何心哉。外廷之臣。不能以诚信感君。以致阻碍。固其罪也。攀缘之徒亦岂诚心爱君者乎。是欲凭藉恩宠。求济其私耳。且其初心。只欲求济其私耳。非必预畜乱国之谋也。利害之际。事势迫蹙则何事不可忍为。自己卯来。士林间祸败之巨者。无不由是而翻覆。故事关宫闱。莫不寒心。 殿下无意惩艾。反或崇长。不肯扫革前弊。祸乱何时而止乎。除官拜职。自有公论。责在铨衡。而特命或出于物情之外。听讼理冤。自有情实。任在有司。而判断或及于细琐之事。群听疑怪。莫知端倪。涓涓不绝则将至滔天。炎炎不灭则终至燎原。可不戒哉。朝廷之上。有腹心之臣。有耳目之官。有喉舌之地。腹心可以谋议。耳目可以闻见。喉舌可以出纳。由是而谋议。由是而闻见。由是而出纳。则朝廷之是非。人物之贤否。庶政之利害。其真伪莫得以眩乱。至于号令之际。事正言顺。人心咸服。无所惶惑。而中和可致。灾变可消矣。纪
大。朝廷和泰。由邪径而行则暗昧回谲。矫伪作孽。国家之安危。于斯判矣。理势之必然者。既可易知。往事之已然者。亦多明验。而时君世主。率皆以外廷之相与者。疏而外之。循例相接而已。以宫闱之攀缘者。亲而信之。倚任听从。是何心哉。外廷之臣。不能以诚信感君。以致阻碍。固其罪也。攀缘之徒亦岂诚心爱君者乎。是欲凭藉恩宠。求济其私耳。且其初心。只欲求济其私耳。非必预畜乱国之谋也。利害之际。事势迫蹙则何事不可忍为。自己卯来。士林间祸败之巨者。无不由是而翻覆。故事关宫闱。莫不寒心。 殿下无意惩艾。反或崇长。不肯扫革前弊。祸乱何时而止乎。除官拜职。自有公论。责在铨衡。而特命或出于物情之外。听讼理冤。自有情实。任在有司。而判断或及于细琐之事。群听疑怪。莫知端倪。涓涓不绝则将至滔天。炎炎不灭则终至燎原。可不戒哉。朝廷之上。有腹心之臣。有耳目之官。有喉舌之地。腹心可以谋议。耳目可以闻见。喉舌可以出纳。由是而谋议。由是而闻见。由是而出纳。则朝廷之是非。人物之贤否。庶政之利害。其真伪莫得以眩乱。至于号令之际。事正言顺。人心咸服。无所惶惑。而中和可致。灾变可消矣。纪晦斋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4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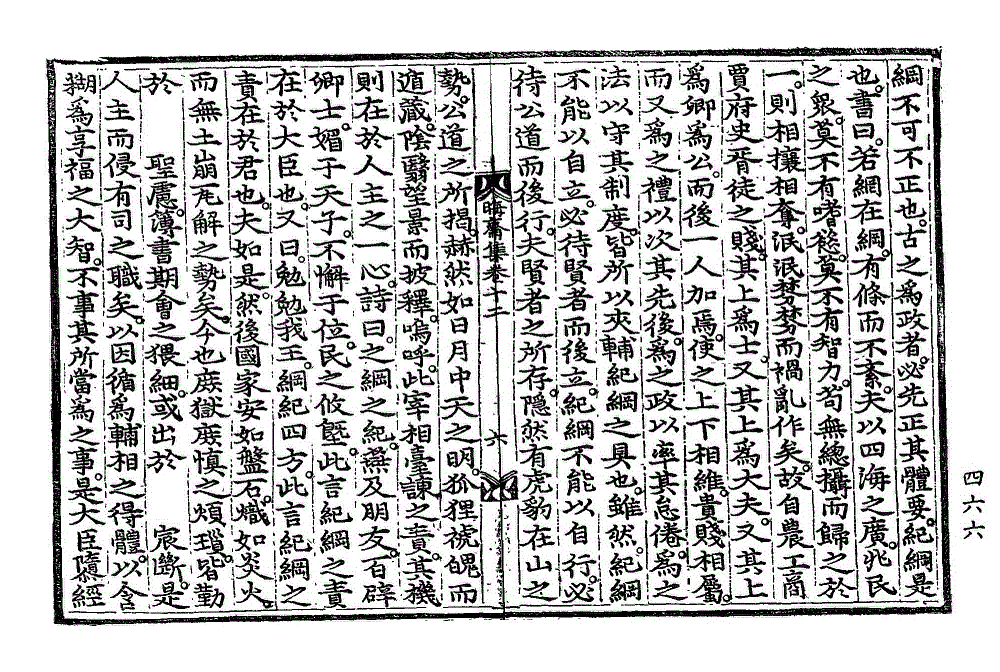 纲不可不正也。古之为政者。必先正其体要。纪纲是也。书曰。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莫不有嗜欲。莫不有智力。苟无总摄而归之于一。则相攘相夺。泯泯棼棼而祸乱作矣。故自农工商贾府史胥徒之贱。其上为士。又其上为大夫。又其上为卿为公。而后一人加焉。使之上下相维。贵贱相属。而又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法以守其制度。皆所以夹辅纪纲之具也。虽然。纪纲不能以自立。必待贤者而后立。纪纲不能以自行。必待公道而后行。夫贤者之所存。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公道之所揭。赫然如日月中天之明。狐狸褫魄而遁藏。阴翳望景而披释。呜呼。此宰相台谏之责。其机则在于人主之一心。诗曰。之纲之纪。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懈于位。民之攸塈。此言纪纲之责在于大臣也。又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此言纪纲之责在于君也。夫如是。然后国家安如盘石。炽如炎火。而无土崩瓦解之势矣。今也庶狱庶慎之烦琐。皆勤于 圣虑。簿书期会之猥细。或出于 宸断。是人主而侵有司之职矣。以因循为辅相之得体。以含糊为享福之大智。不事其所当为之事。是大臣隳经
纲不可不正也。古之为政者。必先正其体要。纪纲是也。书曰。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莫不有嗜欲。莫不有智力。苟无总摄而归之于一。则相攘相夺。泯泯棼棼而祸乱作矣。故自农工商贾府史胥徒之贱。其上为士。又其上为大夫。又其上为卿为公。而后一人加焉。使之上下相维。贵贱相属。而又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法以守其制度。皆所以夹辅纪纲之具也。虽然。纪纲不能以自立。必待贤者而后立。纪纲不能以自行。必待公道而后行。夫贤者之所存。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公道之所揭。赫然如日月中天之明。狐狸褫魄而遁藏。阴翳望景而披释。呜呼。此宰相台谏之责。其机则在于人主之一心。诗曰。之纲之纪。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懈于位。民之攸塈。此言纪纲之责在于大臣也。又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此言纪纲之责在于君也。夫如是。然后国家安如盘石。炽如炎火。而无土崩瓦解之势矣。今也庶狱庶慎之烦琐。皆勤于 圣虑。簿书期会之猥细。或出于 宸断。是人主而侵有司之职矣。以因循为辅相之得体。以含糊为享福之大智。不事其所当为之事。是大臣隳经晦斋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4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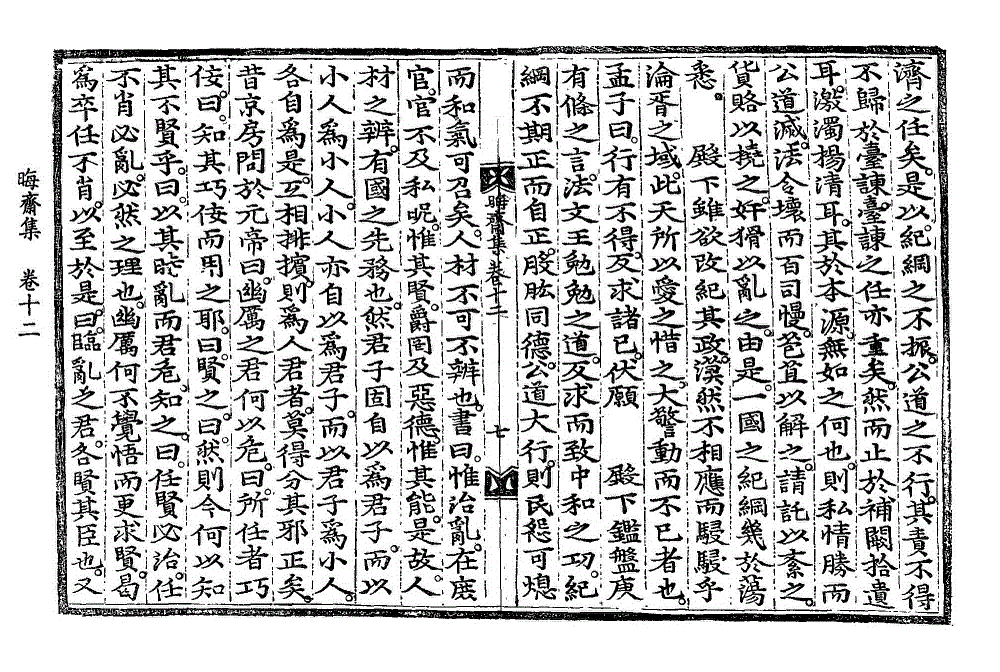 济之任矣。是以。纪纲之不振。公道之不行。其责不得不归于台谏。台谏之任亦重矣。然而止于补阙拾遗耳。激浊扬清耳。其于本源。无如之何也。则私情胜而公道灭。法令坏而百司慢。苞苴以解之。请托以紊之。货赂以挠之。奸猾以乱之。由是。一国之纪纲几于荡悉。 殿下虽欲改纪其政。漠然不相应而骎骎乎沦胥之域。此天所以爱之惜之。大警动而不已者也。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伏愿 殿下鉴盘庚有条之言。法文王勉勉之道。反求而致中和之功。纪纲不期正而自正。股肱同德。公道大行。则民怨可熄而和气可召矣。人材不可不辨也。书曰。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贤。爵罔及恶德。惟其能。是故。人材之辨。有国之先务也。然君子固自以为君子。而以小人为小人。小人亦自以为君子。而以君子为小人。各自为是。互相排摈。则为人君者。莫得分其邪正矣。昔京房问于元帝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曰。所任者巧佞。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曰。贤之。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乎。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曰。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理也。幽厉何不觉悟而更求贤。曷为卒任不肖。以至于是。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也。又
济之任矣。是以。纪纲之不振。公道之不行。其责不得不归于台谏。台谏之任亦重矣。然而止于补阙拾遗耳。激浊扬清耳。其于本源。无如之何也。则私情胜而公道灭。法令坏而百司慢。苞苴以解之。请托以紊之。货赂以挠之。奸猾以乱之。由是。一国之纪纲几于荡悉。 殿下虽欲改纪其政。漠然不相应而骎骎乎沦胥之域。此天所以爱之惜之。大警动而不已者也。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伏愿 殿下鉴盘庚有条之言。法文王勉勉之道。反求而致中和之功。纪纲不期正而自正。股肱同德。公道大行。则民怨可熄而和气可召矣。人材不可不辨也。书曰。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贤。爵罔及恶德。惟其能。是故。人材之辨。有国之先务也。然君子固自以为君子。而以小人为小人。小人亦自以为君子。而以君子为小人。各自为是。互相排摈。则为人君者。莫得分其邪正矣。昔京房问于元帝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曰。所任者巧佞。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曰。贤之。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乎。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曰。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理也。幽厉何不觉悟而更求贤。曷为卒任不肖。以至于是。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也。又晦斋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4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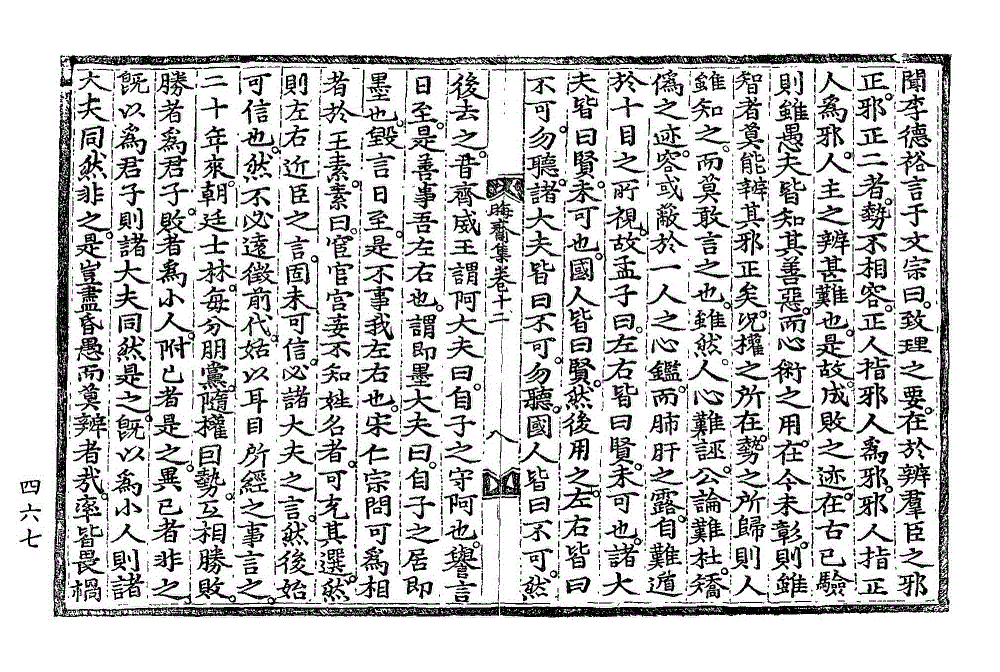 闻李德裕言于文宗曰。致理之要。在于辨群臣之邪正。邪正二者。势不相容。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指正人为邪。人主之辨甚难也。是故。成败之迹。在古已验则虽愚夫皆知其善恶。而心术之用。在今未彰。则虽智者莫能辨其邪正矣。况权之所在。势之所归则人虽知之。而莫敢言之也。虽然。人心难诬。公论难杜。矫伪之迹。容或蔽于一人之心鉴。而肺肝之露。自难遁于十目之所视。故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去之。昔齐威王谓阿大夫曰。自子之守阿也。誉言日至。是善事吾左右也。谓即墨大夫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是不事我左右也。宋仁宗问可为相者于王素。素曰。宦官宫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选。然则左右近臣之言。固未可信。必诸大夫之言。然后始可信也。然不必远徵前代。姑以耳目所经之事言之。二十年来。朝廷士林。每分朋党。随权因势。互相胜败。胜者为君子。败者为小人。附己者是之。异己者非之。既以为君子则诸大夫同然是之。既以为小人则诸大夫同然非之。是岂尽昏愚而莫辨者哉。率皆畏祸
闻李德裕言于文宗曰。致理之要。在于辨群臣之邪正。邪正二者。势不相容。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指正人为邪。人主之辨甚难也。是故。成败之迹。在古已验则虽愚夫皆知其善恶。而心术之用。在今未彰。则虽智者莫能辨其邪正矣。况权之所在。势之所归则人虽知之。而莫敢言之也。虽然。人心难诬。公论难杜。矫伪之迹。容或蔽于一人之心鉴。而肺肝之露。自难遁于十目之所视。故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去之。昔齐威王谓阿大夫曰。自子之守阿也。誉言日至。是善事吾左右也。谓即墨大夫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是不事我左右也。宋仁宗问可为相者于王素。素曰。宦官宫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选。然则左右近臣之言。固未可信。必诸大夫之言。然后始可信也。然不必远徵前代。姑以耳目所经之事言之。二十年来。朝廷士林。每分朋党。随权因势。互相胜败。胜者为君子。败者为小人。附己者是之。异己者非之。既以为君子则诸大夫同然是之。既以为小人则诸大夫同然非之。是岂尽昏愚而莫辨者哉。率皆畏祸晦斋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468H 页
 而附势也。有所论执则大臣率六曹。言官合两司。当此之时。 殿下岂不以为物情如此哉。诸大夫之言。容有不可信者如此。故至于国人皆以为然。然后其论公矣。古人云。谋从众则合天心。为人君。固当大开言路。使国人无大小贵贱。皆得进其言。虽有所犯触。亦不加罪则公论始可闻也。物情始可知也。虽然。孟子必曰国人皆曰贤。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国人皆曰不可。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必察之于己。亲见其贤否之实。然后始决其用舍之分则于贤者。知之深而任之重。不才者不得以幸进矣。故书曰。庶言同则绎。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然则必学问高明。心德昭朗。如鉴之空。如水之澄。然后人心之邪正曲直。莫得以遁其毫发矣。若在我者不能昭明澄澈。而遽欲察之于庶言之外。则或不免偏见之失当。反不如众论之多中矣。故或精鉴于己。或博采于人。内外交證。权衡得宜。然后庶几不失其实矣。近者贤邪稍分。朝廷稍安。但可因是而善持。岂容更鼓其异说。然人心之操舍不常。世道之翻覆无穷。于此而尤加省念。绝偏党之私而守进退之公。则可以致中和而天人胥悦。灾不为灾矣。祭祀不可不谨也。
而附势也。有所论执则大臣率六曹。言官合两司。当此之时。 殿下岂不以为物情如此哉。诸大夫之言。容有不可信者如此。故至于国人皆以为然。然后其论公矣。古人云。谋从众则合天心。为人君。固当大开言路。使国人无大小贵贱。皆得进其言。虽有所犯触。亦不加罪则公论始可闻也。物情始可知也。虽然。孟子必曰国人皆曰贤。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国人皆曰不可。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必察之于己。亲见其贤否之实。然后始决其用舍之分则于贤者。知之深而任之重。不才者不得以幸进矣。故书曰。庶言同则绎。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然则必学问高明。心德昭朗。如鉴之空。如水之澄。然后人心之邪正曲直。莫得以遁其毫发矣。若在我者不能昭明澄澈。而遽欲察之于庶言之外。则或不免偏见之失当。反不如众论之多中矣。故或精鉴于己。或博采于人。内外交證。权衡得宜。然后庶几不失其实矣。近者贤邪稍分。朝廷稍安。但可因是而善持。岂容更鼓其异说。然人心之操舍不常。世道之翻覆无穷。于此而尤加省念。绝偏党之私而守进退之公。则可以致中和而天人胥悦。灾不为灾矣。祭祀不可不谨也。晦斋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4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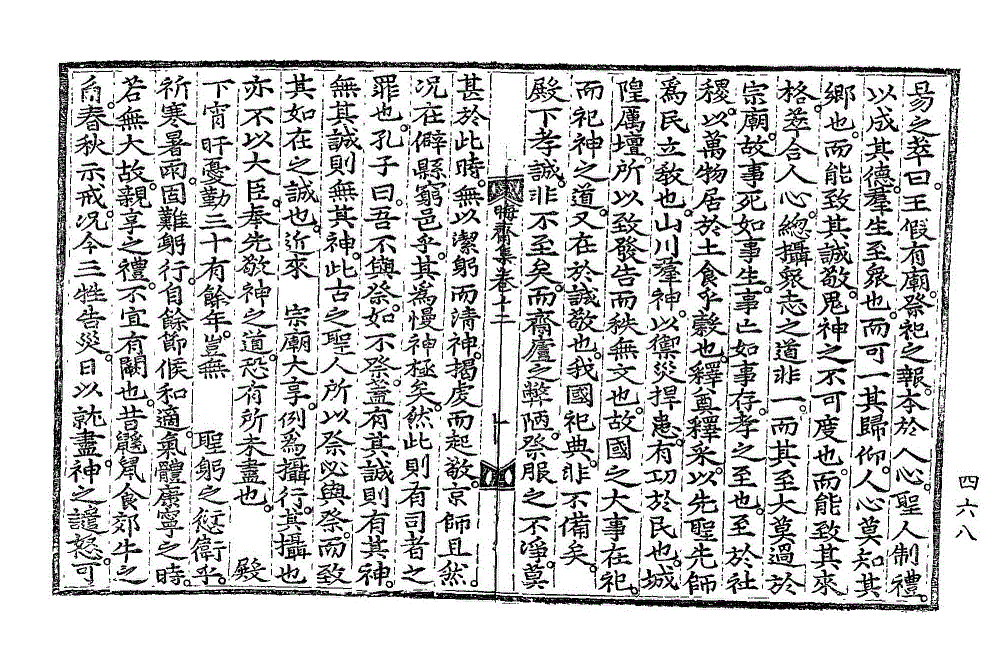 易之萃曰。王假有庙。祭祀之报。本于人心。圣人制礼。以成其德。群生至众也。而可一其归仰。人心莫知其乡也。而能致其诚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来格。萃合人心。总摄众志之道非一。而其至大莫过于宗庙。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至于社稷。以万物居于土食乎谷也。释奠释采。以先圣先师为民立教也。山川群神。以御灾捍患。有功于民也。城隍厉坛。所以致发告而秩无文也。故国之大事在祀。而祀神之道。又在于诚敬也。我国祀典。非不备矣。 殿下孝诚。非不至矣。而斋庐之弊陋。祭服之不净。莫甚于此时。无以洁躬而清神。揭虔而起敬。京师且然。况在僻县穷邑乎。其为慢神极矣。然此则有司者之罪也。孔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盖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此古之圣人所以祭必与祭。而致其如在之诚也。近来 宗庙大享。例为摄行。其摄也亦不以大臣。奉先敬神之道。恐有所未尽也。 殿下宵旰忧勤三十有馀年。岂无 圣躬之愆卫乎。祈寒暑雨。固难躬行。自馀节候和适。气体康宁之时。若无大故。亲享之礼。不宜有阙也。昔鼷鼠食郊牛之角。春秋示戒。况今三牲告灾。日以就尽。神之谴怒。可
易之萃曰。王假有庙。祭祀之报。本于人心。圣人制礼。以成其德。群生至众也。而可一其归仰。人心莫知其乡也。而能致其诚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来格。萃合人心。总摄众志之道非一。而其至大莫过于宗庙。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至于社稷。以万物居于土食乎谷也。释奠释采。以先圣先师为民立教也。山川群神。以御灾捍患。有功于民也。城隍厉坛。所以致发告而秩无文也。故国之大事在祀。而祀神之道。又在于诚敬也。我国祀典。非不备矣。 殿下孝诚。非不至矣。而斋庐之弊陋。祭服之不净。莫甚于此时。无以洁躬而清神。揭虔而起敬。京师且然。况在僻县穷邑乎。其为慢神极矣。然此则有司者之罪也。孔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盖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此古之圣人所以祭必与祭。而致其如在之诚也。近来 宗庙大享。例为摄行。其摄也亦不以大臣。奉先敬神之道。恐有所未尽也。 殿下宵旰忧勤三十有馀年。岂无 圣躬之愆卫乎。祈寒暑雨。固难躬行。自馀节候和适。气体康宁之时。若无大故。亲享之礼。不宜有阙也。昔鼷鼠食郊牛之角。春秋示戒。况今三牲告灾。日以就尽。神之谴怒。可晦斋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4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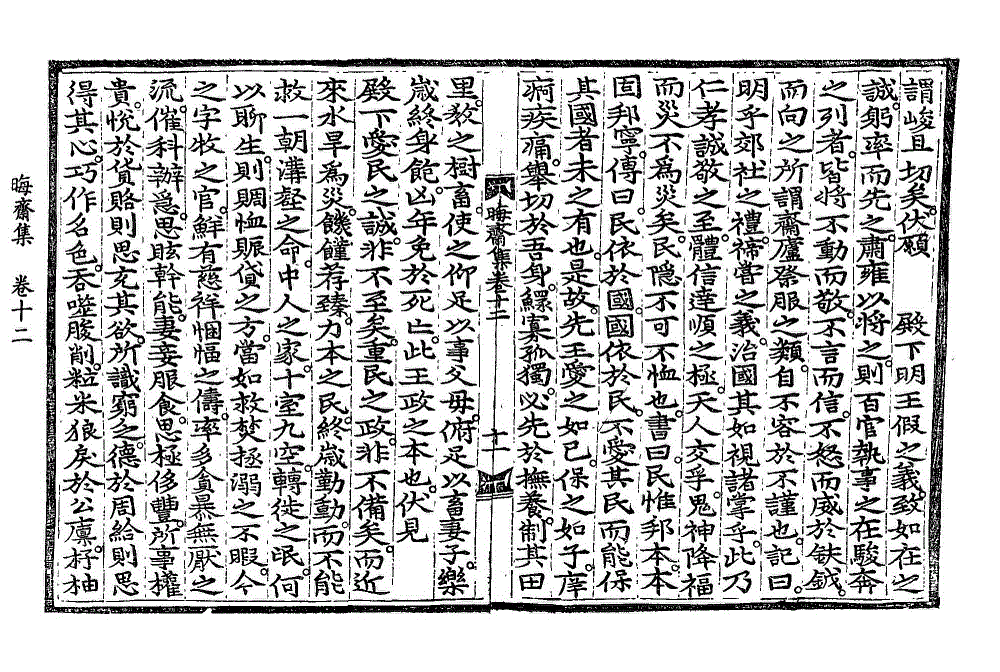 谓峻且切矣。伏愿 殿下明王假之义。致如在之诚。躬率而先之。肃雍以将之。则百官执事之在骏奔之列者。皆将不动而敬。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于鈇钺。而向之所谓斋庐祭服之类。自不容于不谨也。记曰。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视诸掌乎。此乃仁孝诚敬之至。体信达顺之极。天人交孚。鬼神降福而灾不为灾矣。民隐不可不恤也。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传曰。民依于国。国依于民。不爱其民而能保其国者未之有也。是故。先王爱之如己。保之如子。庠痾疾痛。举切于吾身。鳏寡孤独。必先于抚养。制其田里。教之树畜。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此王政之本也。伏见 殿下爱民之诚。非不至矣。重民之政。非不备矣。而近来水旱为灾。饥馑荐臻。力本之民。终岁勤动。而不能救一朝沟壑之命。中人之家。十室九空。转徙之氓。何以聊生。则赒恤赈贷之方。当如救焚拯溺之不暇。今之字牧之官。鲜有慈祥悃愊之俦。率多贪暴无厌之流。催科办急。思眩干能。妻妾服食。思极侈丰。所事权贵。悦于货赂则思充其欲。所识穷乏。德于周给则思得其心。巧作名色。吞噬朘削。粒米狼戾于公廪。杼柚
谓峻且切矣。伏愿 殿下明王假之义。致如在之诚。躬率而先之。肃雍以将之。则百官执事之在骏奔之列者。皆将不动而敬。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于鈇钺。而向之所谓斋庐祭服之类。自不容于不谨也。记曰。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视诸掌乎。此乃仁孝诚敬之至。体信达顺之极。天人交孚。鬼神降福而灾不为灾矣。民隐不可不恤也。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传曰。民依于国。国依于民。不爱其民而能保其国者未之有也。是故。先王爱之如己。保之如子。庠痾疾痛。举切于吾身。鳏寡孤独。必先于抚养。制其田里。教之树畜。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此王政之本也。伏见 殿下爱民之诚。非不至矣。重民之政。非不备矣。而近来水旱为灾。饥馑荐臻。力本之民。终岁勤动。而不能救一朝沟壑之命。中人之家。十室九空。转徙之氓。何以聊生。则赒恤赈贷之方。当如救焚拯溺之不暇。今之字牧之官。鲜有慈祥悃愊之俦。率多贪暴无厌之流。催科办急。思眩干能。妻妾服食。思极侈丰。所事权贵。悦于货赂则思充其欲。所识穷乏。德于周给则思得其心。巧作名色。吞噬朘削。粒米狼戾于公廪。杼柚晦斋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4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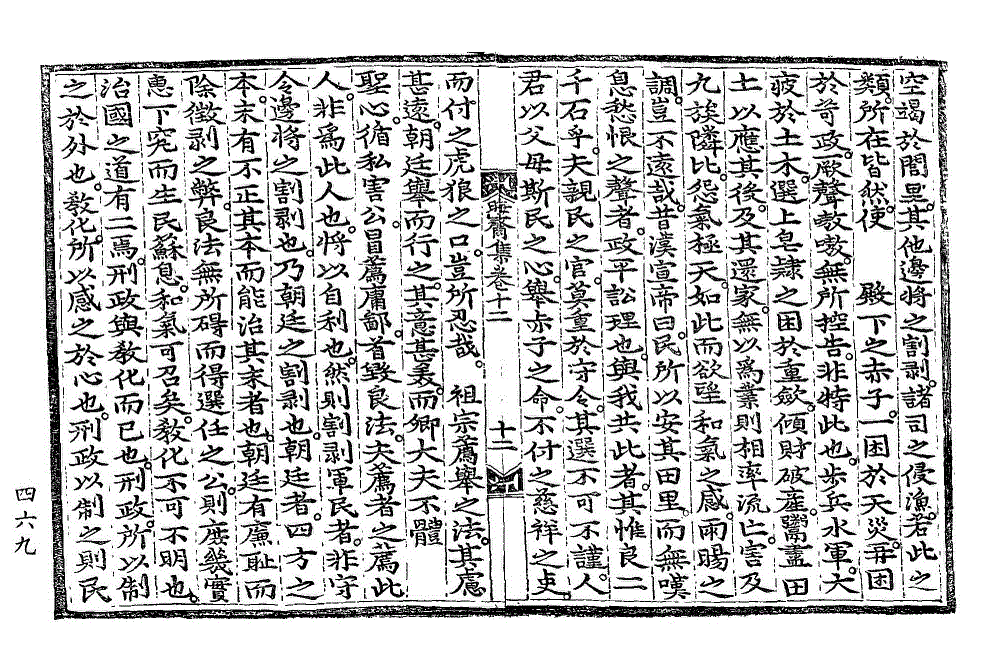 空竭于闾里。其他边将之割剥。诸司之侵渔。若此之类。所在皆然。使 殿下之赤子。一困于天灾。再困于苛政。厥声嗷嗷。无所控告。非特此也。步兵水军。大疲于土木。选上皂隶之困于重敛。倾财破产。鬻尽田土以应其役。及其还家。无以为业则相率流亡。害及九族邻比。怨气极天。如此而欲望和气之感。雨旸之调。岂不远哉。昔汉宣帝曰。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声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夫亲民之官。莫重于守令。其选不可不谨。人君以父母斯民之心。举赤子之命。不付之慈祥之吏。而付之虎狼之口。岂所忍哉。祖宗荐举之法。其虑甚远。朝廷举而行之。其意甚美。而卿大夫不体 圣心。循私害公。冒荐庸鄙。首毁良法。夫荐者之荐此人。非为此人也。将以自利也。然则割剥军民者。非守令边将之割剥也。乃朝廷之割剥也。朝廷者。四方之本。末有不正其本而能治其末者也。朝廷有廉耻而除徵剥之弊。良法无所碍而得选任之公。则庶几实惠下究而生民苏息。和气可召矣。教化不可不明也。治国之道有二焉。刑政与教化而已也。刑政。所以制之于外也。教化。所以感之于心也。刑政以制之则民
空竭于闾里。其他边将之割剥。诸司之侵渔。若此之类。所在皆然。使 殿下之赤子。一困于天灾。再困于苛政。厥声嗷嗷。无所控告。非特此也。步兵水军。大疲于土木。选上皂隶之困于重敛。倾财破产。鬻尽田土以应其役。及其还家。无以为业则相率流亡。害及九族邻比。怨气极天。如此而欲望和气之感。雨旸之调。岂不远哉。昔汉宣帝曰。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声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夫亲民之官。莫重于守令。其选不可不谨。人君以父母斯民之心。举赤子之命。不付之慈祥之吏。而付之虎狼之口。岂所忍哉。祖宗荐举之法。其虑甚远。朝廷举而行之。其意甚美。而卿大夫不体 圣心。循私害公。冒荐庸鄙。首毁良法。夫荐者之荐此人。非为此人也。将以自利也。然则割剥军民者。非守令边将之割剥也。乃朝廷之割剥也。朝廷者。四方之本。末有不正其本而能治其末者也。朝廷有廉耻而除徵剥之弊。良法无所碍而得选任之公。则庶几实惠下究而生民苏息。和气可召矣。教化不可不明也。治国之道有二焉。刑政与教化而已也。刑政。所以制之于外也。教化。所以感之于心也。刑政以制之则民晦斋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4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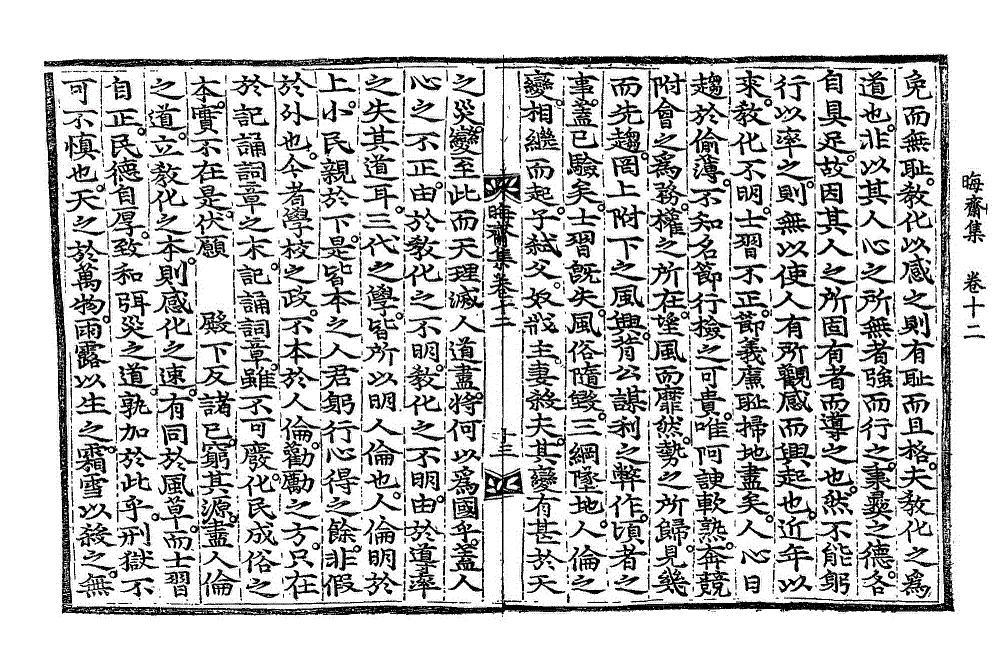 免而无耻。教化以感之则有耻而且格。夫教化之为道也。非以其人心之所无者强而行之。秉彝之德。各自具足。故因其人之所固有者而导之也。然不能躬行以率之。则无以使人有所观感而兴起也。近年以来。教化不明。士习不正。节义廉耻扫地尽矣。人心日趋于偷薄。不知名节行检之可贵。唯阿谀软熟。奔竞附会之为务。权之所在。望风而靡然。势之所归。见几而先趋。罔上附下之风兴。背公谋利之弊作。顷者之事。盖已验矣。士习既失。风俗随毁。三纲坠地。人伦之变。相继而起。子弑父。奴戕主。妻杀夫。其变有甚于天之灾。变至此而天理灭人道尽。将何以为国乎。盖人心之不正。由于教化之不明。教化之不明。由于导率之失其道耳。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是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馀。非假于外也。今者学校之政。不本于人伦。劝励之方。只在于记诵词章之末。记诵词章。虽不可废。化民成俗之本。实不在是。伏愿 殿下反诸己。穷其源。尽人伦之道。立教化之本。则感化之速。有同于风草。而士习自正。民德自厚。致和弭灾之道。孰加于此乎。刑狱不可不慎也。天之于万物。雨露以生之。霜雪以杀之。无
免而无耻。教化以感之则有耻而且格。夫教化之为道也。非以其人心之所无者强而行之。秉彝之德。各自具足。故因其人之所固有者而导之也。然不能躬行以率之。则无以使人有所观感而兴起也。近年以来。教化不明。士习不正。节义廉耻扫地尽矣。人心日趋于偷薄。不知名节行检之可贵。唯阿谀软熟。奔竞附会之为务。权之所在。望风而靡然。势之所归。见几而先趋。罔上附下之风兴。背公谋利之弊作。顷者之事。盖已验矣。士习既失。风俗随毁。三纲坠地。人伦之变。相继而起。子弑父。奴戕主。妻杀夫。其变有甚于天之灾。变至此而天理灭人道尽。将何以为国乎。盖人心之不正。由于教化之不明。教化之不明。由于导率之失其道耳。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是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馀。非假于外也。今者学校之政。不本于人伦。劝励之方。只在于记诵词章之末。记诵词章。虽不可废。化民成俗之本。实不在是。伏愿 殿下反诸己。穷其源。尽人伦之道。立教化之本。则感化之速。有同于风草。而士习自正。民德自厚。致和弭灾之道。孰加于此乎。刑狱不可不慎也。天之于万物。雨露以生之。霜雪以杀之。无晦斋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4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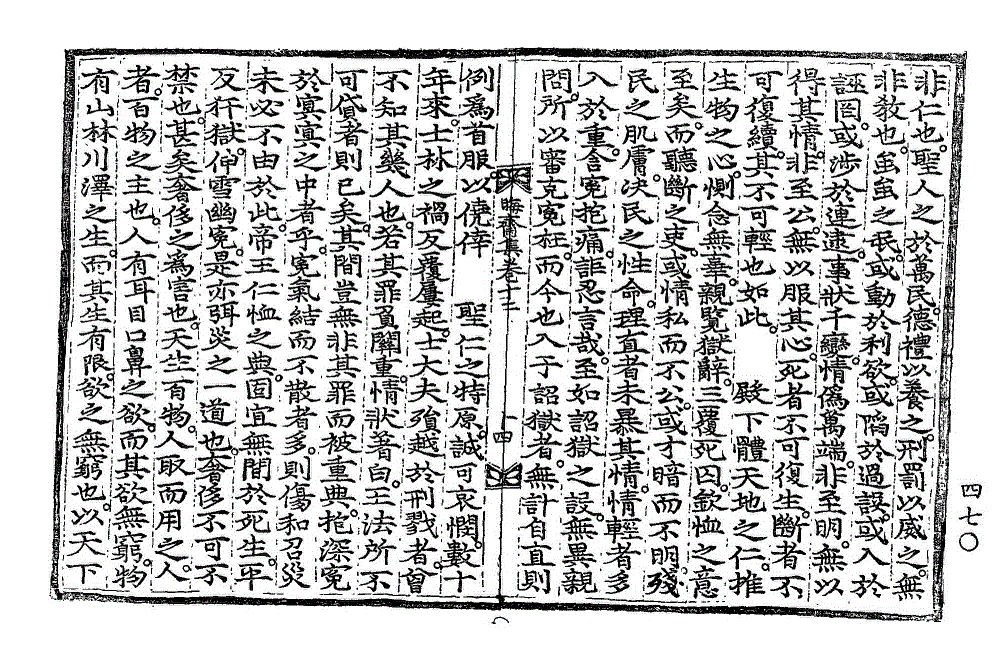 非仁也。圣人之于万民。德礼以养之。刑罚以威之。无非教也。蚩蚩之氓。或动于利欲。或陷于过误。或入于诬罔。或涉于连逮。事状千变。情伪万端。非至明。无以得其情。非至公。无以服其心。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其不可轻也如此。 殿下体天地之仁。推生物之心。恻念无辜。亲览狱辞。三覆死囚。钦恤之意至矣。而听断之吏。或情私而不公。或才暗而不明。残民之肌肤。决民之性命。理直者未暴其情。情轻者多入于重。含冤抱痛。讵忍言哉。至如诏狱之设。无异亲问。所以审克冤枉。而今也入于诏狱者。无计自直则例为首服。以侥倖 圣仁之特原。诚可哀悯。数十年来。士林之祸反覆屡起。士大夫殒越于刑戮者。曾不知其几人也。若其罪负关重。情状著白。王法所不可贷者则已矣。其间岂无非其罪而被重典。抱深冤于冥冥之中者乎。冤气结而不散者多。则伤和召灾未必不由于此。帝王仁恤之典。固宜无间于死生。平反犴狱。伸雪幽冤。是亦弭灾之一道也。奢侈不可不禁也。甚矣奢侈之为害也。天生百物。人取而用之。人者。百物之主也。人有耳目口鼻之欲。而其欲无穷。物有山林川泽之生。而其生有限。欲之无穷也。以天下
非仁也。圣人之于万民。德礼以养之。刑罚以威之。无非教也。蚩蚩之氓。或动于利欲。或陷于过误。或入于诬罔。或涉于连逮。事状千变。情伪万端。非至明。无以得其情。非至公。无以服其心。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其不可轻也如此。 殿下体天地之仁。推生物之心。恻念无辜。亲览狱辞。三覆死囚。钦恤之意至矣。而听断之吏。或情私而不公。或才暗而不明。残民之肌肤。决民之性命。理直者未暴其情。情轻者多入于重。含冤抱痛。讵忍言哉。至如诏狱之设。无异亲问。所以审克冤枉。而今也入于诏狱者。无计自直则例为首服。以侥倖 圣仁之特原。诚可哀悯。数十年来。士林之祸反覆屡起。士大夫殒越于刑戮者。曾不知其几人也。若其罪负关重。情状著白。王法所不可贷者则已矣。其间岂无非其罪而被重典。抱深冤于冥冥之中者乎。冤气结而不散者多。则伤和召灾未必不由于此。帝王仁恤之典。固宜无间于死生。平反犴狱。伸雪幽冤。是亦弭灾之一道也。奢侈不可不禁也。甚矣奢侈之为害也。天生百物。人取而用之。人者。百物之主也。人有耳目口鼻之欲。而其欲无穷。物有山林川泽之生。而其生有限。欲之无穷也。以天下晦斋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4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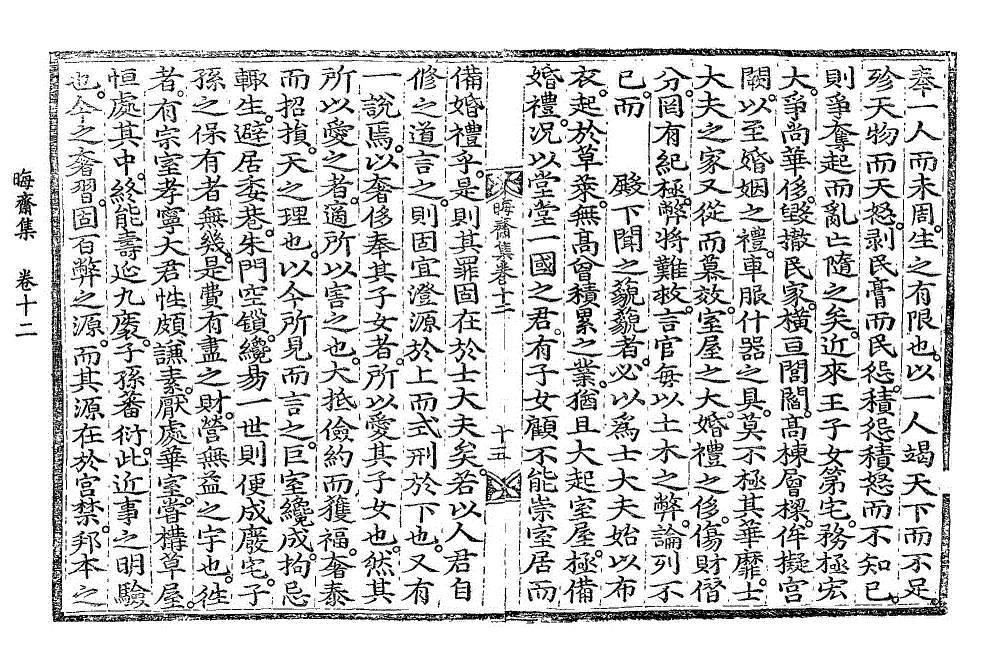 奉一人而未周。生之有限也。以一人竭天下而不足。殄天物而天怒。剥民膏而民怨。积怨积怒而不知已。则争夺起而乱亡随之矣。近来王子女第宅。务极宏大。争尚华侈。毁撤民家。横亘闾阎。高栋层梁。侔拟宫阙。以至婚姻之礼。车服什器之具。莫不极其华靡。士大夫之家又从而慕效。室屋之大。婚礼之侈。伤财僭分。罔有纪极。弊将难救。言官每以土木之弊。论列不已。而 殿下闻之藐藐者。必以为士大夫始以布衣。起于草莱。无高曾积累之业。犹且大起室屋。极备婚礼。况以堂堂一国之君。有子女顾不能崇室居而备婚礼乎。是则其罪固在于士大夫矣。若以人君自修之道言之。则固宜澄源于上而式刑于下也。又有一说焉。以奢侈奉其子女者。所以爱其子女也。然其所以爱之者。适所以害之也。大抵俭约而获福。奢泰而招损。天之理也。以今所见而言之。巨室才成。拘忌辄生。避居委巷。朱门空锁。才易一世则便成废宅。子孙之保有者无几。是费有尽之财。营无益之宇也。往者。有宗室孝宁大君性颇谦素。厌处华室。尝构草屋。恒处其中。终能寿延九帙。子孙蕃衍。此近事之明验也。今之奢习。固百弊之源。而其源在于宫禁。邦本之
奉一人而未周。生之有限也。以一人竭天下而不足。殄天物而天怒。剥民膏而民怨。积怨积怒而不知已。则争夺起而乱亡随之矣。近来王子女第宅。务极宏大。争尚华侈。毁撤民家。横亘闾阎。高栋层梁。侔拟宫阙。以至婚姻之礼。车服什器之具。莫不极其华靡。士大夫之家又从而慕效。室屋之大。婚礼之侈。伤财僭分。罔有纪极。弊将难救。言官每以土木之弊。论列不已。而 殿下闻之藐藐者。必以为士大夫始以布衣。起于草莱。无高曾积累之业。犹且大起室屋。极备婚礼。况以堂堂一国之君。有子女顾不能崇室居而备婚礼乎。是则其罪固在于士大夫矣。若以人君自修之道言之。则固宜澄源于上而式刑于下也。又有一说焉。以奢侈奉其子女者。所以爱其子女也。然其所以爱之者。适所以害之也。大抵俭约而获福。奢泰而招损。天之理也。以今所见而言之。巨室才成。拘忌辄生。避居委巷。朱门空锁。才易一世则便成废宅。子孙之保有者无几。是费有尽之财。营无益之宇也。往者。有宗室孝宁大君性颇谦素。厌处华室。尝构草屋。恒处其中。终能寿延九帙。子孙蕃衍。此近事之明验也。今之奢习。固百弊之源。而其源在于宫禁。邦本之晦斋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471L 页
 凋瘁。府库之虚竭。皆由于此。亦足以起怨而致灾。伏惟 殿下深省焉。谏诤不可不纳也。人主不能自聪。必合众听而为聪。不能自明。必合众视而为明。古之圣王。其聪明思虑固非庸众人所能助其一端。而犹且乐受人之谏者。嗜善无穷也。 殿下躬上圣之资。有好问之德。凡有论列阙失。受以为过而自责。成汤之弗咈。无以加矣。顷年以来。从谏之美。寖不如初。訑訑之色。或形于外。进言之际。但示优容。而无采用之实。遇灾责躬。专事虚文而无求言之 旨。无乃有厌闻直言。吝于改过之意乎。非特此也。台谏如有论执稍坚。违忤 上旨者。则辄出 特命。遽迁他职。虽无形迹可以指论。物情或不能无疑也。顷者求言之后。上书者偶触忌讳。辄欲加罪。至命三省而推鞫。或有系贱而言事者。以为欲乱朝廷者教之。是以求言为阱于国中也。各陈所怀。容有不当之论。人君但当择其善而用之而已。岂宜加怒于妄言之人乎。谏者非人臣之利。乃国家之福也。苟以言被罪则谁肯犯雷霆之威。进无益之言乎。顷者。国柄落于奸手。危亡在于朝夕。人莫敢进一言以触之者以此也。当此之时。有能斥言其情状者。则非徒触奸凶之锋。亦且
凋瘁。府库之虚竭。皆由于此。亦足以起怨而致灾。伏惟 殿下深省焉。谏诤不可不纳也。人主不能自聪。必合众听而为聪。不能自明。必合众视而为明。古之圣王。其聪明思虑固非庸众人所能助其一端。而犹且乐受人之谏者。嗜善无穷也。 殿下躬上圣之资。有好问之德。凡有论列阙失。受以为过而自责。成汤之弗咈。无以加矣。顷年以来。从谏之美。寖不如初。訑訑之色。或形于外。进言之际。但示优容。而无采用之实。遇灾责躬。专事虚文而无求言之 旨。无乃有厌闻直言。吝于改过之意乎。非特此也。台谏如有论执稍坚。违忤 上旨者。则辄出 特命。遽迁他职。虽无形迹可以指论。物情或不能无疑也。顷者求言之后。上书者偶触忌讳。辄欲加罪。至命三省而推鞫。或有系贱而言事者。以为欲乱朝廷者教之。是以求言为阱于国中也。各陈所怀。容有不当之论。人君但当择其善而用之而已。岂宜加怒于妄言之人乎。谏者非人臣之利。乃国家之福也。苟以言被罪则谁肯犯雷霆之威。进无益之言乎。顷者。国柄落于奸手。危亡在于朝夕。人莫敢进一言以触之者以此也。当此之时。有能斥言其情状者。则非徒触奸凶之锋。亦且晦斋先生集卷之十二 第 4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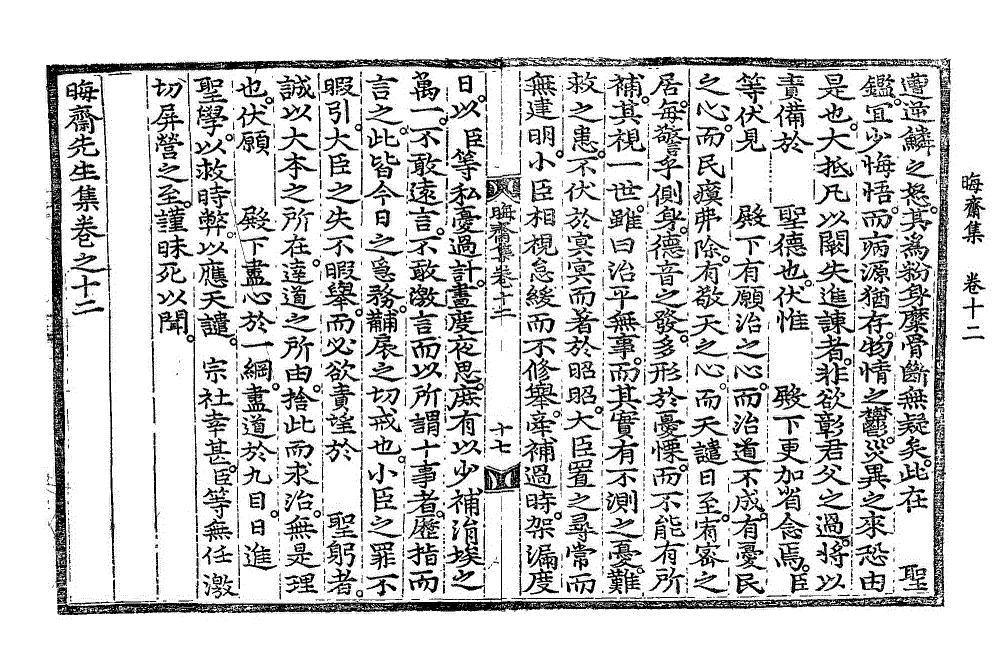 遭逆鳞之怒。其为粉身糜骨断无疑矣。此在 圣鉴。宜少悔悟。而病源犹存。物情之郁。灾异之来恐由是也。大抵凡以阙失进谏者。非欲彰君父之过。将以责备于 圣德也。伏惟 殿下更加省念焉。臣等伏见 殿下有愿治之心。而治道不成。有忧民之心。而民瘼弗除。有敬天之心。而天谴日至。宥密之居。每警乎侧身。德音之发。多形于忧慄。而不能有所补。其视一世。虽曰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难救之患。不伏于冥冥而著于昭昭。大臣置之寻常而无建明。小臣相视怠缓而不修举。牵补过时。架漏度日。以臣等私忧过计。昼度夜思。庶有以少补涓埃之万一。不敢远言。不敢激言而以所谓十事者。历指而言之。此皆今日之急务。黼扆之切戒也。小臣之罪不暇引。大臣之失不暇举。而必欲责望于 圣躬者。诚以大本之所在。达道之所由。舍此而求治。无是理也。伏愿 殿下尽心于一纲。尽道于九目。日进 圣学。以救时弊。以应天谴。 宗社幸甚。臣等无任激切屏营之至。谨昧死以闻。
遭逆鳞之怒。其为粉身糜骨断无疑矣。此在 圣鉴。宜少悔悟。而病源犹存。物情之郁。灾异之来恐由是也。大抵凡以阙失进谏者。非欲彰君父之过。将以责备于 圣德也。伏惟 殿下更加省念焉。臣等伏见 殿下有愿治之心。而治道不成。有忧民之心。而民瘼弗除。有敬天之心。而天谴日至。宥密之居。每警乎侧身。德音之发。多形于忧慄。而不能有所补。其视一世。虽曰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难救之患。不伏于冥冥而著于昭昭。大臣置之寻常而无建明。小臣相视怠缓而不修举。牵补过时。架漏度日。以臣等私忧过计。昼度夜思。庶有以少补涓埃之万一。不敢远言。不敢激言而以所谓十事者。历指而言之。此皆今日之急务。黼扆之切戒也。小臣之罪不暇引。大臣之失不暇举。而必欲责望于 圣躬者。诚以大本之所在。达道之所由。舍此而求治。无是理也。伏愿 殿下尽心于一纲。尽道于九目。日进 圣学。以救时弊。以应天谴。 宗社幸甚。臣等无任激切屏营之至。谨昧死以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