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静庵先生续集附录卷之二 第 x 页
静庵先生续集附录卷之二
疏○劄○启
疏○劄○启
静庵先生续集附录卷之二 第 1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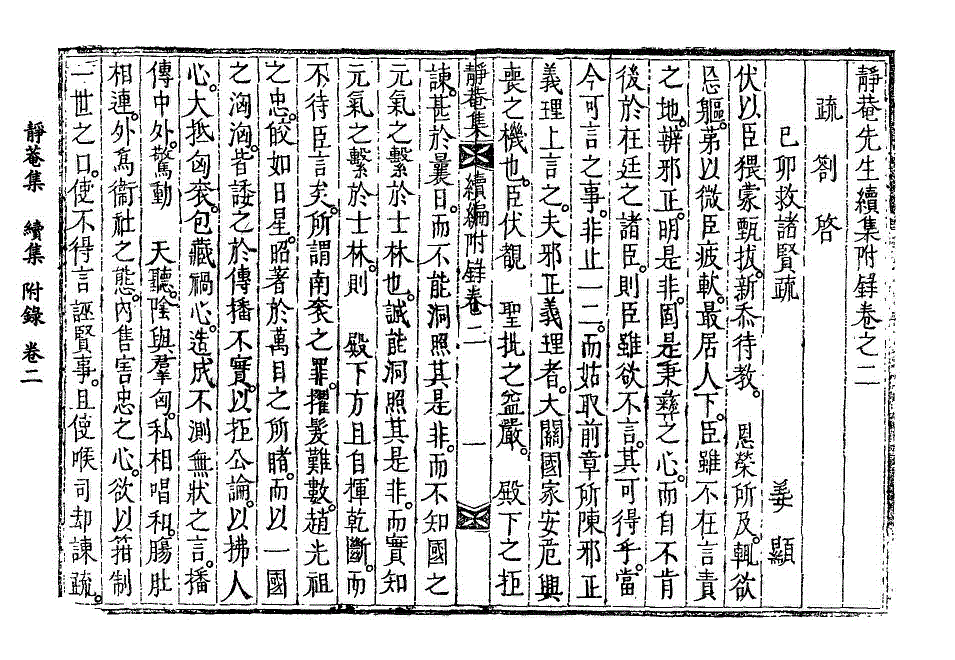 己卯救诸贤疏(姜 显)
己卯救诸贤疏(姜 显)伏以臣猥蒙甄拔。新忝待教。 恩荣所及。辄欲忘躯。第以微臣疲软。最居人下。臣虽不在言责之地。辨邪正。明是非。固是秉彝之心。而自不肯后于在廷之诸臣。则臣虽欲不言。其可得乎。当今可言之事。非止一二。而姑取前章所陈邪正义理上言之。夫邪正义理者。大关国家安危兴丧之机也。臣伏睹 圣批之益严。 殿下之拒谏。甚于曩日。而不能洞照其是非。而不知国之元气之系于士林也。诚能洞照其是非。而实知元气之系于士林。则 殿下方且自挥乾断。而不待臣言矣。所谓南衮之罪。擢发难数。赵光祖之忠。皎如日星。昭著于万目之所睹。而以一国之汹汹。皆诿之于传播不实。以拒公论。以拂人心。大抵匈衮。包藏祸心。造成不测无状之言。播传中外。惊动 天听。阴与群匈。私相唱和。肠肚相连。外为卫社之态。内售害忠之心。欲以钳制一世之口。使不得言诬贤事。且使喉司却谏疏。
静庵先生续集附录卷之二 第 1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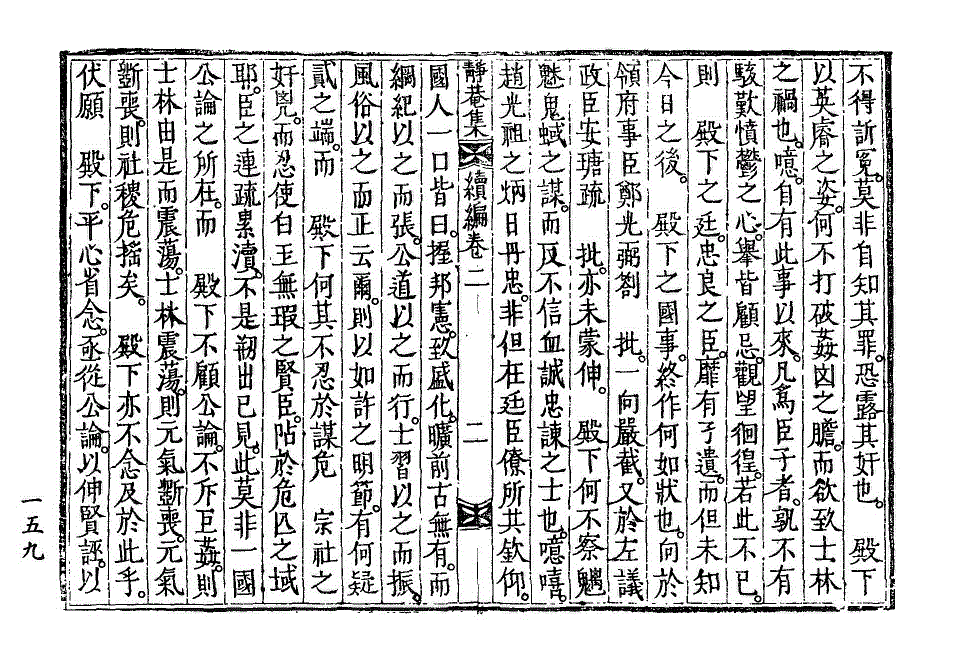 不得诉冤。莫非自知其罪。恐露其奸也。 殿下以英睿之姿。何不打破奸凶之胆。而欲致士林之祸也。噫。自有此事以来。凡为臣子者。孰不有骇叹愤郁之心。举皆顾忌。观望徊徨。若此不已。则 殿下之廷。忠良之臣。靡有孑遗。而但未知今日之后。 殿下之国事。终作何如状也。向于领府事臣郑光弼劄 批。一向严截。又于左议政臣安瑭疏 批。亦未蒙伸。 殿下何不察魑魅鬼蜮之谋。而反不信血诚忠谏之士也。噫嘻。赵光祖之炳日丹忠。非但在廷臣僚所共钦仰。国人一口皆曰。握邦宪。致盛化。旷前古无有。而纲纪以之而张。公道以之而行。士习以之而振。风俗以之而正云尔。则以如许之明节。有何疑贰之端。而 殿下何其不忍于谋危 宗社之奸凶。而忍使白玉无瑕之贤臣。阽于危亡之域耶。臣之连疏累渎。不是刱出己见。此莫非一国公论之所在。而 殿下不顾公论。不斥巨奸。则士林由是而震荡。士林震荡。则元气斲丧。元气斲丧。则社稷危摇矣。 殿下亦不念及于此乎。伏愿 殿下。平心省念。亟从公论。以伸贤诬。以
不得诉冤。莫非自知其罪。恐露其奸也。 殿下以英睿之姿。何不打破奸凶之胆。而欲致士林之祸也。噫。自有此事以来。凡为臣子者。孰不有骇叹愤郁之心。举皆顾忌。观望徊徨。若此不已。则 殿下之廷。忠良之臣。靡有孑遗。而但未知今日之后。 殿下之国事。终作何如状也。向于领府事臣郑光弼劄 批。一向严截。又于左议政臣安瑭疏 批。亦未蒙伸。 殿下何不察魑魅鬼蜮之谋。而反不信血诚忠谏之士也。噫嘻。赵光祖之炳日丹忠。非但在廷臣僚所共钦仰。国人一口皆曰。握邦宪。致盛化。旷前古无有。而纲纪以之而张。公道以之而行。士习以之而振。风俗以之而正云尔。则以如许之明节。有何疑贰之端。而 殿下何其不忍于谋危 宗社之奸凶。而忍使白玉无瑕之贤臣。阽于危亡之域耶。臣之连疏累渎。不是刱出己见。此莫非一国公论之所在。而 殿下不顾公论。不斥巨奸。则士林由是而震荡。士林震荡。则元气斲丧。元气斲丧。则社稷危摇矣。 殿下亦不念及于此乎。伏愿 殿下。平心省念。亟从公论。以伸贤诬。以静庵先生续集附录卷之二 第 1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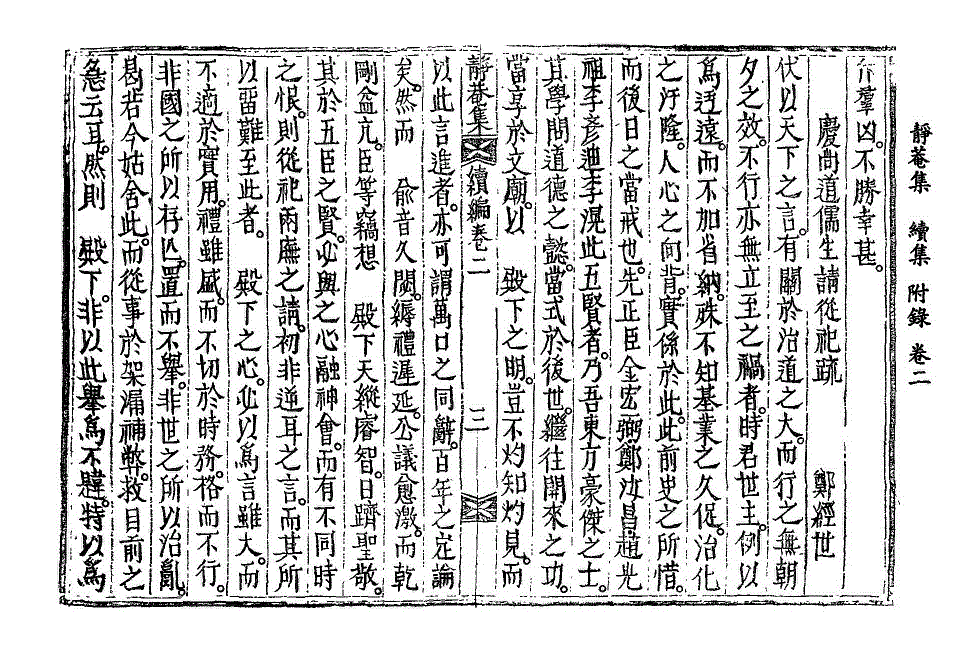 斥群凶。不胜幸甚。
斥群凶。不胜幸甚。庆尚道儒生请从祀疏(郑经世)
伏以天下之言。有关于治道之大。而行之无朝夕之效。不行亦无立至之祸者。时君世主。例以为迂远。而不加省纳。殊不知基业之久促。治化之污隆。人心之向背。实系于此。此前史之所惜。而后日之当戒也。先正臣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李彦迪,李滉此五贤者。乃吾东方豪杰之士。其学问道德之懿。当式于后世。继往开来之功。当享于文庙。以 殿下之明。岂不灼知灼见。而以此言进者。亦可谓万口之同辞。百年之定论矣。然而 俞音久閟。缛礼迟延。公议愈激。而乾刚益亢。臣等窃想 殿下天纵睿智。日跻圣敬。其于五臣之贤。必与之心融神会。而有不同时之恨。则从祀两庑之请。初非逆耳之言。而其所以留难至此者。 殿下之心。必以为言虽大。而不适于实用。礼虽盛。而不切于时务。格而不行。非国之所以存亡。置而不举。非世之所以治乱。曷若今姑舍此。而从事于架漏补弊。救目前之急云耳。然则 殿下。非以此举为不韪。特以为
静庵先生续集附录卷之二 第 1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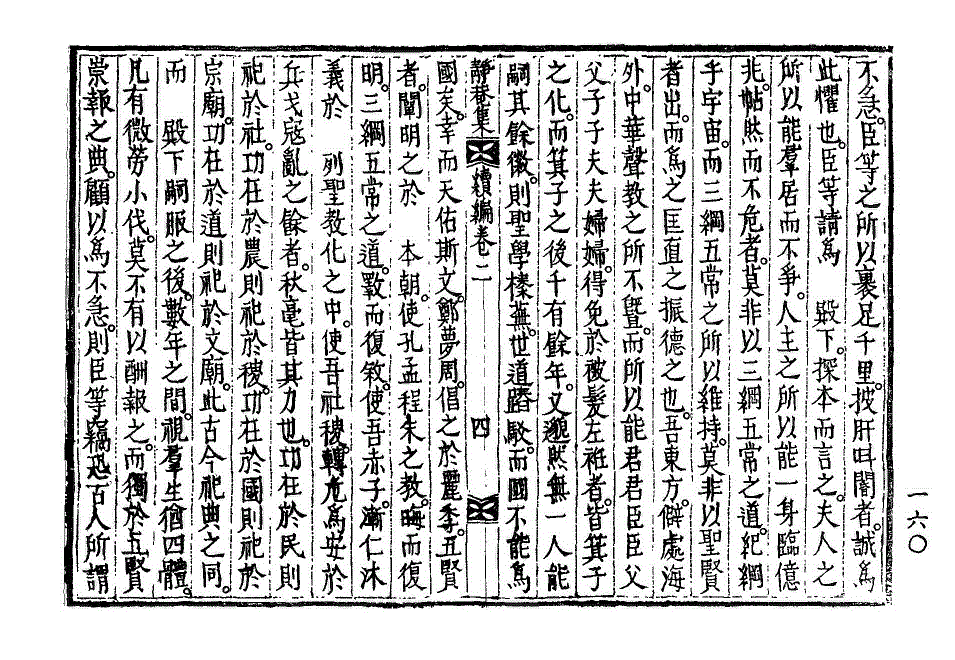 不急。臣等之所以裹足千里。披肝叫阍者。诚为此惧也。臣等请为 殿下。探本而言之。夫人之所以能群居而不争。人主之所以能一身临亿兆。帖然而不危者。莫非以三纲五常之道。纪纲乎宇宙。而三纲五常之所以维持。莫非以圣贤者出。而为之匡直之振德之也。吾东方。僻处海外。中华声教之所不暨。而所以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得免于被发左衽者。皆箕子之化。而箕子之后千有馀年。又邈然无一人能嗣其馀徽。则圣学榛芜。世道舛驳。而国不能为国矣。幸而天佑斯文。郑梦周。倡之于丽季。五贤者。阐明之于 本朝。使孔孟程朱之教。晦而复明。三纲五常之道。斁而复叙。使吾赤子。渐仁沐义于 列圣教化之中。使吾社稷。转危为安于兵戈寇乱之馀者。秋毫皆其力也。功在于民则祀于社。功在于农则祀于稷。功在于国则祀于宗庙。功在于道则祀于文庙。此古今祀典之同。而 殿下嗣服之后。数年之间。视群生犹四体。凡有微劳小伐。莫不有以酬报之。而独于五贤崇报之典。顾以为不急。则臣等窃恐古人所谓
不急。臣等之所以裹足千里。披肝叫阍者。诚为此惧也。臣等请为 殿下。探本而言之。夫人之所以能群居而不争。人主之所以能一身临亿兆。帖然而不危者。莫非以三纲五常之道。纪纲乎宇宙。而三纲五常之所以维持。莫非以圣贤者出。而为之匡直之振德之也。吾东方。僻处海外。中华声教之所不暨。而所以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得免于被发左衽者。皆箕子之化。而箕子之后千有馀年。又邈然无一人能嗣其馀徽。则圣学榛芜。世道舛驳。而国不能为国矣。幸而天佑斯文。郑梦周。倡之于丽季。五贤者。阐明之于 本朝。使孔孟程朱之教。晦而复明。三纲五常之道。斁而复叙。使吾赤子。渐仁沐义于 列圣教化之中。使吾社稷。转危为安于兵戈寇乱之馀者。秋毫皆其力也。功在于民则祀于社。功在于农则祀于稷。功在于国则祀于宗庙。功在于道则祀于文庙。此古今祀典之同。而 殿下嗣服之后。数年之间。视群生犹四体。凡有微劳小伐。莫不有以酬报之。而独于五贤崇报之典。顾以为不急。则臣等窃恐古人所谓静庵先生续集附录卷之二 第 1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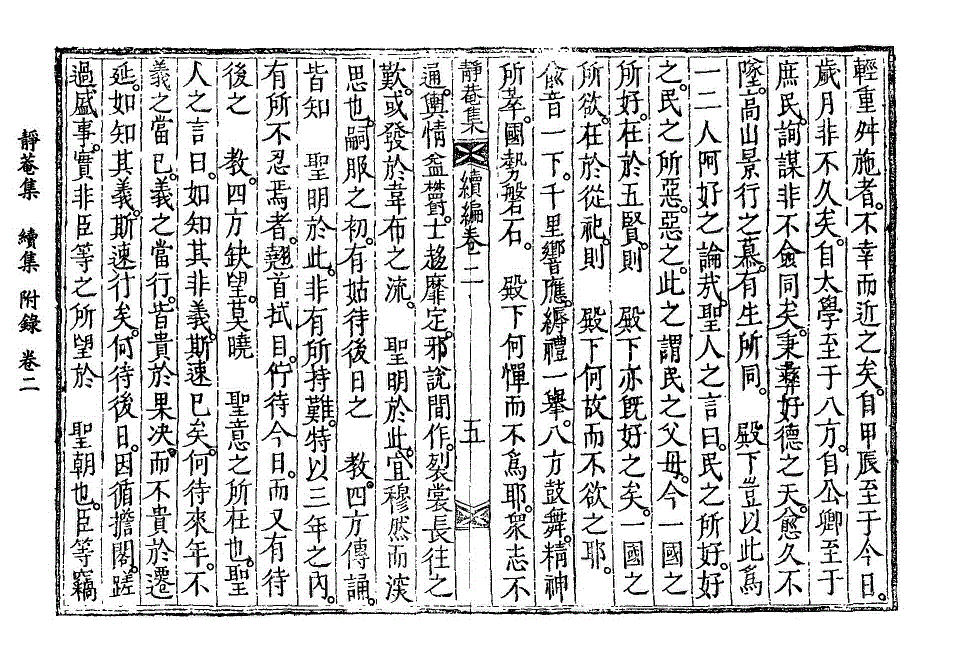 轻重舛施者。不幸而近之矣。自甲辰至于今日。岁月非不久矣。自太学至于八方。自公卿至于庶民。询谋非不佥同矣。秉彝好德之天。愈久不坠。高山景行之慕。有生所同。 殿下岂以此为一二人阿好之论哉。圣人之言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今一国之所好。在于五贤。则 殿下亦既好之矣。一国之所欲。在于从祀。则 殿下何故而不欲之耶。 俞音一下。千里响应。缛礼一举。八方鼓舞。精神所萃。国势磐石。 殿下何惮而不为耶。众志不通。舆情益郁。士趋靡定。邪说间作。裂裳长往之叹。或发于韦布之流。 圣明于此。宜穆然而深思也。嗣服之初。有姑待后日之 教。四方传诵。皆知 圣明于此。非有所持难。特以三年之内。有所不忍焉者。翘首拭目。伫待今日。而又有待后之 教。四方缺望。莫晓 圣意之所在也。圣人之言曰。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不义之当已。义之当行。皆贵于果决。而不贵于迁延。如知其义。斯速行矣。何待后日。因循担阁。蹉过盛事。实非臣等之所望于 圣朝也。臣等窃
轻重舛施者。不幸而近之矣。自甲辰至于今日。岁月非不久矣。自太学至于八方。自公卿至于庶民。询谋非不佥同矣。秉彝好德之天。愈久不坠。高山景行之慕。有生所同。 殿下岂以此为一二人阿好之论哉。圣人之言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今一国之所好。在于五贤。则 殿下亦既好之矣。一国之所欲。在于从祀。则 殿下何故而不欲之耶。 俞音一下。千里响应。缛礼一举。八方鼓舞。精神所萃。国势磐石。 殿下何惮而不为耶。众志不通。舆情益郁。士趋靡定。邪说间作。裂裳长往之叹。或发于韦布之流。 圣明于此。宜穆然而深思也。嗣服之初。有姑待后日之 教。四方传诵。皆知 圣明于此。非有所持难。特以三年之内。有所不忍焉者。翘首拭目。伫待今日。而又有待后之 教。四方缺望。莫晓 圣意之所在也。圣人之言曰。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不义之当已。义之当行。皆贵于果决。而不贵于迁延。如知其义。斯速行矣。何待后日。因循担阁。蹉过盛事。实非臣等之所望于 圣朝也。臣等窃静庵先生续集附录卷之二 第 1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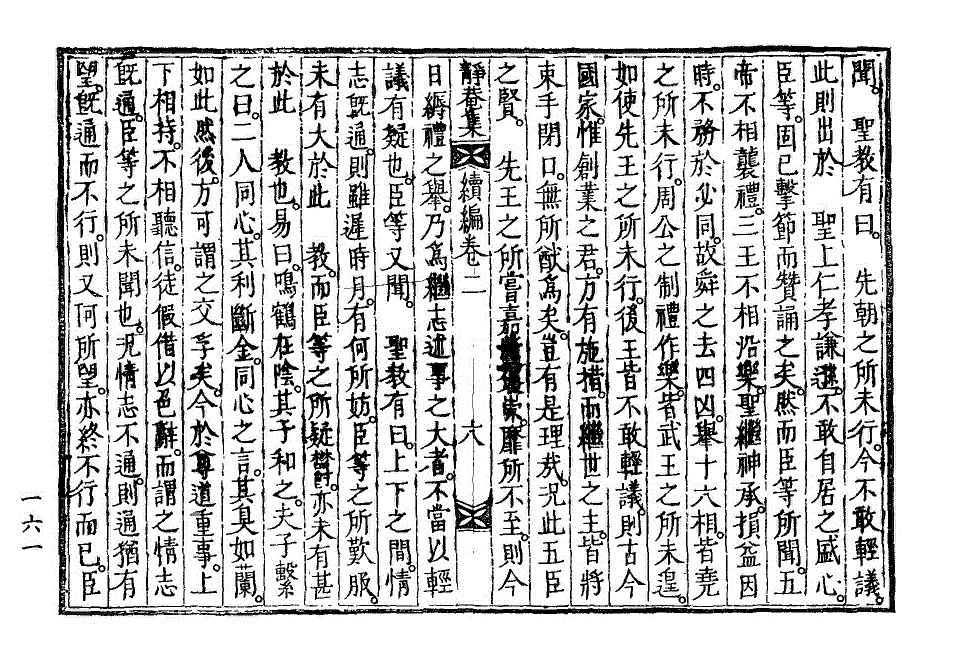 闻。 圣教有曰。 先朝之所未行。今不敢轻议。此则出于 圣上仁孝谦逊。不敢自居之盛心。臣等。固已击节而赞诵之矣。然而臣等所闻。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沿乐。圣继神承。损益因时。不务于必同。故舜之去四凶。举十六相。皆尧之所未行。周公之制礼作乐。皆武王之所未遑。如使先王之所未行。后王皆不敢轻议。则古今国家。惟创业之君。方有施措。而继世之主。皆将束手闭口。无所猷为矣。岂有是理哉。况此五臣之贤。 先王之所尝嘉赏褒崇。靡所不至。则今日缛礼之举。乃为继志述事之大者。不当以轻议有疑也。臣等又闻。 圣教有曰。上下之间。情志既通。则虽迟时月。有何所妨。臣等之所叹服。未有大于此 教。而臣等之所疑郁。亦未有甚于此 教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夫子系之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如此然后。方可谓之交孚矣。今于尊道重事。上下相持。不相听信。徒假借以色辞。而谓之情志既通。臣等之所未闻也。况情志不通。则通犹有望。既通而不行。则又何所望。亦终不行而已。臣
闻。 圣教有曰。 先朝之所未行。今不敢轻议。此则出于 圣上仁孝谦逊。不敢自居之盛心。臣等。固已击节而赞诵之矣。然而臣等所闻。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沿乐。圣继神承。损益因时。不务于必同。故舜之去四凶。举十六相。皆尧之所未行。周公之制礼作乐。皆武王之所未遑。如使先王之所未行。后王皆不敢轻议。则古今国家。惟创业之君。方有施措。而继世之主。皆将束手闭口。无所猷为矣。岂有是理哉。况此五臣之贤。 先王之所尝嘉赏褒崇。靡所不至。则今日缛礼之举。乃为继志述事之大者。不当以轻议有疑也。臣等又闻。 圣教有曰。上下之间。情志既通。则虽迟时月。有何所妨。臣等之所叹服。未有大于此 教。而臣等之所疑郁。亦未有甚于此 教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夫子系之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如此然后。方可谓之交孚矣。今于尊道重事。上下相持。不相听信。徒假借以色辞。而谓之情志既通。臣等之所未闻也。况情志不通。则通犹有望。既通而不行。则又何所望。亦终不行而已。臣静庵先生续集附录卷之二 第 1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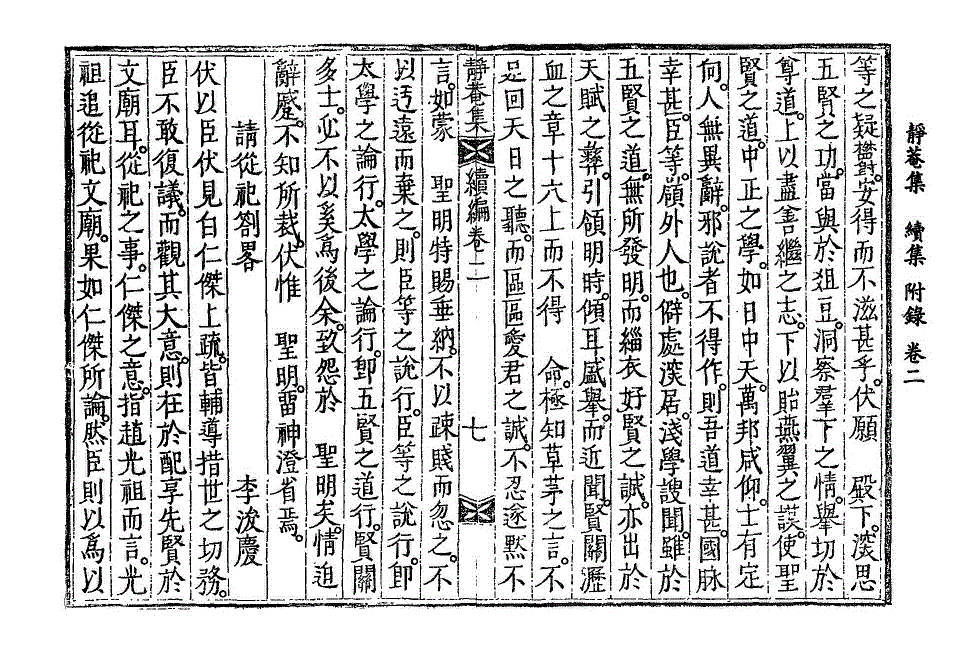 等之疑郁。安得而不滋甚乎。伏愿 殿下。深思五贤之功。当与于俎豆。洞察群下之情。举切于尊道。上以尽善继之志。下以贻燕翼之谟。使圣贤之道。中正之学。如日中天。万邦咸仰。士有定向。人无异辞。邪说者不得作。则吾道幸甚。国脉幸甚。臣等。岭外人也。僻处深居。浅学謏闻。虽于五贤之道。无所发明。而缁衣好贤之诚。亦出于天赋之彝。引领明时。倾耳盛举。而近闻。贤关沥血之章十六上而不得 命。极知草茅之言。不足回天日之听。而区区爱君之诚。不忍遂默不言。如蒙 圣明特赐垂纳。不以疏贱而忽之。不以迂远而弃之。则臣等之说行。臣等之说行。即太学之论行。太学之论行。即五贤之道行。贤关多士。必不以奚为后余。致怨于 圣明矣。情迫辞蹙。不知所裁。伏惟 圣明。留神澄省焉。
等之疑郁。安得而不滋甚乎。伏愿 殿下。深思五贤之功。当与于俎豆。洞察群下之情。举切于尊道。上以尽善继之志。下以贻燕翼之谟。使圣贤之道。中正之学。如日中天。万邦咸仰。士有定向。人无异辞。邪说者不得作。则吾道幸甚。国脉幸甚。臣等。岭外人也。僻处深居。浅学謏闻。虽于五贤之道。无所发明。而缁衣好贤之诚。亦出于天赋之彝。引领明时。倾耳盛举。而近闻。贤关沥血之章十六上而不得 命。极知草茅之言。不足回天日之听。而区区爱君之诚。不忍遂默不言。如蒙 圣明特赐垂纳。不以疏贱而忽之。不以迂远而弃之。则臣等之说行。臣等之说行。即太学之论行。太学之论行。即五贤之道行。贤关多士。必不以奚为后余。致怨于 圣明矣。情迫辞蹙。不知所裁。伏惟 圣明。留神澄省焉。请从祀劄略(李浚庆)
伏以臣伏见白仁杰上疏。皆辅导措世之切务。臣不敢复议。而观其大意。则在于配享先贤于文庙耳。从祀之事。仁杰之意。指赵光祖而言。光祖追从祀文庙。果如仁杰所论。然臣则以为以
静庵先生续集附录卷之二 第 1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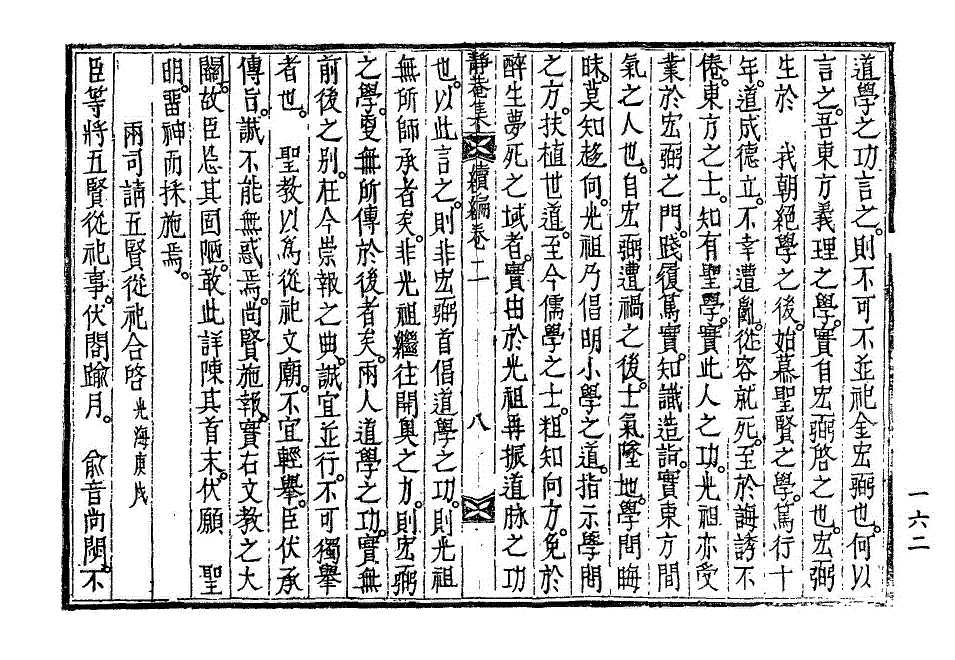 道学之功言之。则不可不并祀金宏弼也。何以言之。吾东方义理之学。实自宏弼启之也。宏弼生于 我朝绝学之后。始慕圣贤之学。笃行十年。道成德立。不幸遭乱。从容就死。至于诲诱不倦。东方之士。知有圣学。实此人之功。光祖亦受业于宏弼之门。践履笃实。知识造诣。实东方间气之人也。自宏弼遭祸之后。士气坠地。学问晦昧。莫知趋向。光祖乃倡明小学之道。指示学问之方。扶植世道。至今儒学之士。粗知向方。免于醉生梦死之域者。实由于光祖再振道脉之功也。以此言之。则非宏弼首倡道学之功。则光祖无所师承者矣。非光祖继往开奥之力。则宏弼之学。更无所传于后者矣。两人道学之功。实无前后之别。在今崇报之典。诚宜并行。不可独举者也。 圣教以为从祀文庙。不宜轻举。臣伏承传旨。诚不能无惑焉。尚贤施报。实右文教之大关。故臣忘其固陋。敢此详陈其首末。伏愿 圣明。留神而采施焉。
道学之功言之。则不可不并祀金宏弼也。何以言之。吾东方义理之学。实自宏弼启之也。宏弼生于 我朝绝学之后。始慕圣贤之学。笃行十年。道成德立。不幸遭乱。从容就死。至于诲诱不倦。东方之士。知有圣学。实此人之功。光祖亦受业于宏弼之门。践履笃实。知识造诣。实东方间气之人也。自宏弼遭祸之后。士气坠地。学问晦昧。莫知趋向。光祖乃倡明小学之道。指示学问之方。扶植世道。至今儒学之士。粗知向方。免于醉生梦死之域者。实由于光祖再振道脉之功也。以此言之。则非宏弼首倡道学之功。则光祖无所师承者矣。非光祖继往开奥之力。则宏弼之学。更无所传于后者矣。两人道学之功。实无前后之别。在今崇报之典。诚宜并行。不可独举者也。 圣教以为从祀文庙。不宜轻举。臣伏承传旨。诚不能无惑焉。尚贤施报。实右文教之大关。故臣忘其固陋。敢此详陈其首末。伏愿 圣明。留神而采施焉。两司请五贤从祀合启(光海庚戌)
臣等将五贤从祀事。伏閤踰月。 俞音尚閟。不
静庵先生续集附录卷之二 第 1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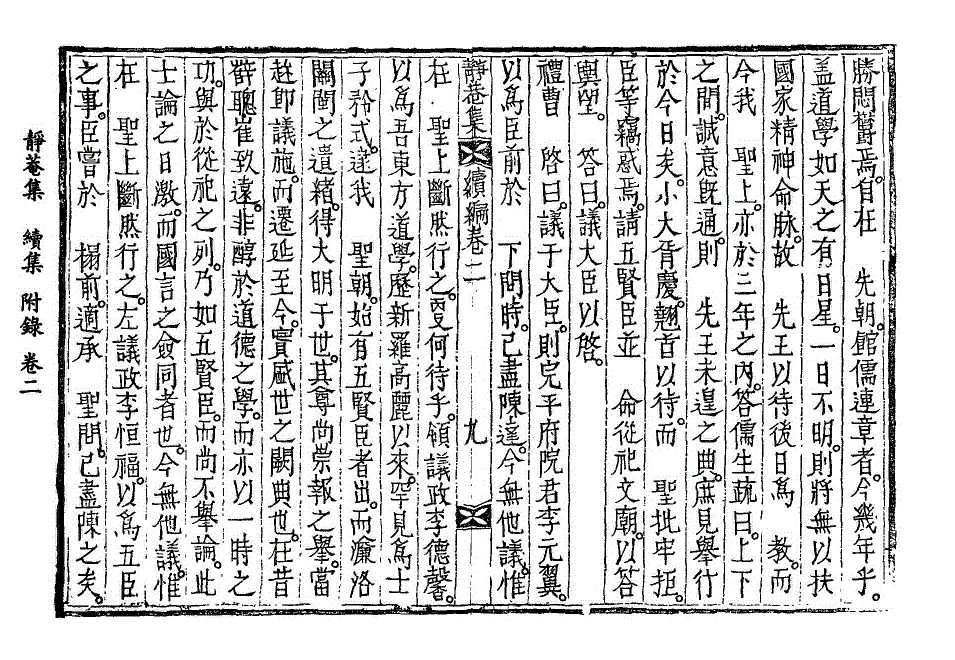 胜闷郁焉。自在 先朝。馆儒连章者。今几年乎。盖道学如天之有日星。一日不明。则将无以扶国家精神命脉。故 先王以待后日为 教。而今我 圣上。亦于三年之内。答儒生疏曰。上下之间。诚意既通。则 先王未遑之典。庶见举行于今日矣。小大胥庆。翘首以待。而 圣批牢拒。臣等窃惑焉。请五贤臣并 命从祀文庙。以答舆望。 答曰。议大臣以启。
胜闷郁焉。自在 先朝。馆儒连章者。今几年乎。盖道学如天之有日星。一日不明。则将无以扶国家精神命脉。故 先王以待后日为 教。而今我 圣上。亦于三年之内。答儒生疏曰。上下之间。诚意既通。则 先王未遑之典。庶见举行于今日矣。小大胥庆。翘首以待。而 圣批牢拒。臣等窃惑焉。请五贤臣并 命从祀文庙。以答舆望。 答曰。议大臣以启。礼曹 启曰。议于大臣。则完平府院君李元翼。以为臣前于 下问时。已尽陈达。今无他议。惟在 圣上断然行之。更何待乎。领议政李德馨。以为吾东方道学。历新罗高丽以来。罕见为士子矜式。逮我 圣朝。始有五贤臣者出。而濂洛关闽之遗绪。得大明于世。其尊尚崇报之举。当趁即议施。而迁延至今。实盛世之阙典也。在昔嶭(一作薛)聪,崔致远。非醇于道德之学。而亦以一时之功。与于从祀之列。乃如五贤臣。而尚不举论。此士论之日激。而国言之佥同者也。今无他议。惟在 圣上断然行之。左议政李恒福。以为五臣之事。臣尝于 榻前。适承 圣问。已尽陈之矣。
静庵先生续集附录卷之二 第 1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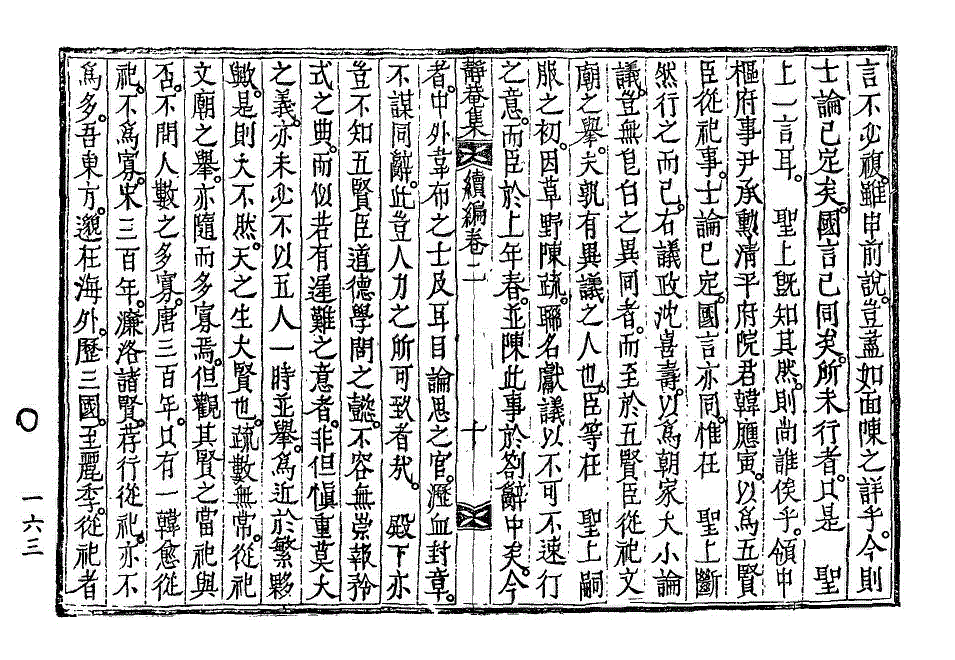 言不必复。虽申前说。岂尽如面陈之详乎。今则士论已定矣。国言已同矣。所未行者。只是 圣上一言耳。 圣上既知其然。则尚谁俟乎。领中枢府事尹承勋,清平府院君韩应寅。以为五贤臣从祀事。士论已定。国言亦同。惟在 圣上断然行之而已。右议政沈喜寿。以为朝家大小论议。岂无皂白之异同者。而至于五贤臣从祀文庙之举。夫孰有异议之人也。臣等在 圣上嗣服之初。因草野陈疏。联名献议以不可不速行之意。而臣于上年春。并陈此事于劄辞中矣。今者。中外韦布之士及耳目论思之官。沥血封章。不谋同辞。此岂人力之所可致者哉。 殿下亦岂不知五贤臣道德学问之懿。不容无崇报矜式之典。而似若有迟难之意者。非但慎重莫大之义。亦未必不以五人一时并举。为近于繁夥欤。是则大不然。天之生大贤也。疏数无常。从祀文庙之举。亦随而多寡焉。但观其贤之当祀与否。不问人数之多寡。唐三百年。只有一韩愈从祀。不为寡。宋三百年。濂洛诸贤。荐行从祀。亦不为多。吾东方。邈在海外。历三国。至丽季。从祀者
言不必复。虽申前说。岂尽如面陈之详乎。今则士论已定矣。国言已同矣。所未行者。只是 圣上一言耳。 圣上既知其然。则尚谁俟乎。领中枢府事尹承勋,清平府院君韩应寅。以为五贤臣从祀事。士论已定。国言亦同。惟在 圣上断然行之而已。右议政沈喜寿。以为朝家大小论议。岂无皂白之异同者。而至于五贤臣从祀文庙之举。夫孰有异议之人也。臣等在 圣上嗣服之初。因草野陈疏。联名献议以不可不速行之意。而臣于上年春。并陈此事于劄辞中矣。今者。中外韦布之士及耳目论思之官。沥血封章。不谋同辞。此岂人力之所可致者哉。 殿下亦岂不知五贤臣道德学问之懿。不容无崇报矜式之典。而似若有迟难之意者。非但慎重莫大之义。亦未必不以五人一时并举。为近于繁夥欤。是则大不然。天之生大贤也。疏数无常。从祀文庙之举。亦随而多寡焉。但观其贤之当祀与否。不问人数之多寡。唐三百年。只有一韩愈从祀。不为寡。宋三百年。濂洛诸贤。荐行从祀。亦不为多。吾东方。邈在海外。历三国。至丽季。从祀者静庵先生续集附录卷之二 第 1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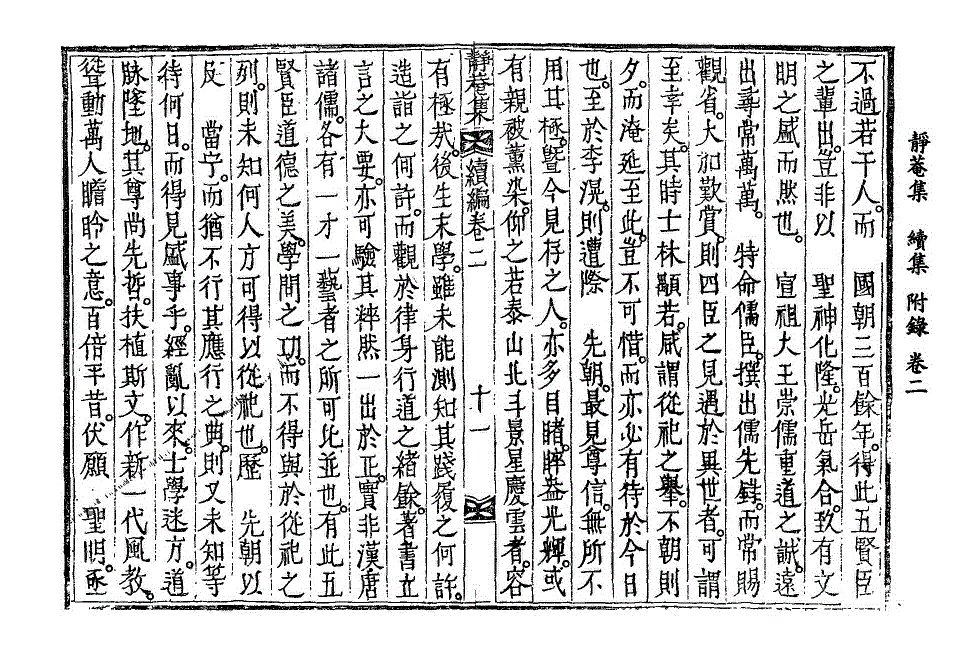 不过若干人。而 国朝三百馀年。得此五贤臣之辈出。岂非以 圣神化隆。光岳气合。致有文明之盛而然也。 宣祖大王崇儒重道之诚。远出寻常万万。 特命儒臣。撰出儒先录。而常赐观省。大加叹赏。则四臣之见遇于异世者。可谓至幸矣。其时士林颙若。咸谓从祀之举。不朝则夕。而淹延至此。岂不可惜。而亦必有待于今日也。至于李滉。则遭际 先朝。最见尊信。无所不用其极。暨今见存之人。亦多目睹。睟盎光辉。或有亲被薰染。仰之若泰山北斗景星庆云者。容有极哉。后生末学。虽未能测知其践履之何许。造诣之何许。而观于律身行道之绪馀。著书立言之大要。亦可验其粹然一出于正。贤非汉,唐诸儒。各有一才一艺者之所可比并也。有此五贤臣道德之美。学问之功。而不得与于从祀之列。则未知何人方可得以从祀也。历 先朝以及 当宁。而犹不行其应行之典。则又未知等待何日。而得见盛事乎。经乱以来。士学迷方。道脉坠地。其尊尚先哲。扶植斯文。作新一代风教。耸动万人瞻聆之意。百倍平昔。伏愿 圣明。亟
不过若干人。而 国朝三百馀年。得此五贤臣之辈出。岂非以 圣神化隆。光岳气合。致有文明之盛而然也。 宣祖大王崇儒重道之诚。远出寻常万万。 特命儒臣。撰出儒先录。而常赐观省。大加叹赏。则四臣之见遇于异世者。可谓至幸矣。其时士林颙若。咸谓从祀之举。不朝则夕。而淹延至此。岂不可惜。而亦必有待于今日也。至于李滉。则遭际 先朝。最见尊信。无所不用其极。暨今见存之人。亦多目睹。睟盎光辉。或有亲被薰染。仰之若泰山北斗景星庆云者。容有极哉。后生末学。虽未能测知其践履之何许。造诣之何许。而观于律身行道之绪馀。著书立言之大要。亦可验其粹然一出于正。贤非汉,唐诸儒。各有一才一艺者之所可比并也。有此五贤臣道德之美。学问之功。而不得与于从祀之列。则未知何人方可得以从祀也。历 先朝以及 当宁。而犹不行其应行之典。则又未知等待何日。而得见盛事乎。经乱以来。士学迷方。道脉坠地。其尊尚先哲。扶植斯文。作新一代风教。耸动万人瞻聆之意。百倍平昔。伏愿 圣明。亟静庵先生续集附录卷之二 第 1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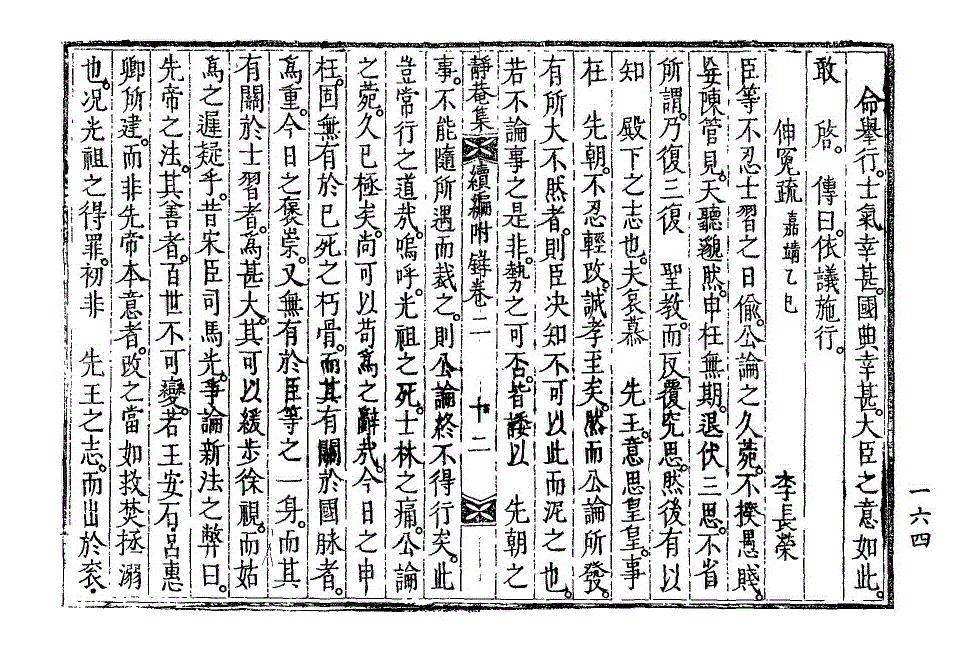 命举行。士气幸甚。国典幸甚。大臣之意如此。敢 启。 传曰。依议施行。
命举行。士气幸甚。国典幸甚。大臣之意如此。敢 启。 传曰。依议施行。伸冤疏(嘉靖乙巳○李长荣)
臣等不忍士习之日偷。公论之久菀。不揆愚贱。妄陈管见。天听邈然。申枉无期。退伏三思。不省所谓。乃复三复 圣教。而反覆究思。然后有以知 殿下之志也。夫哀慕 先王。意思皇皇。事在 先朝。不忍轻改。诚孝至矣。然而公论所发。有所大不然者。则臣决知不可以此而泥之也。若不论事之是非。势之可否。皆诿以 先朝之事。不能随所遇而裁之。则公论终不得行矣。此岂常行之道哉。呜呼。光祖之死。士林之痛。公论之菀。久已极矣。尚可以苟为之辞哉。今日之申枉。固无有于已死之朽骨。而其有关于国脉者。为重。今日之褒崇。又无有于臣等之一身。而其有关于士习者。为甚大。其可以缓步徐视。而姑为之迟疑乎。昔宋臣司马光。争论新法之弊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变。若王安石,吕惠卿所建。而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也。况光祖之得罪。初非 先王之志。而出于衮,
静庵先生续集附录卷之二 第 1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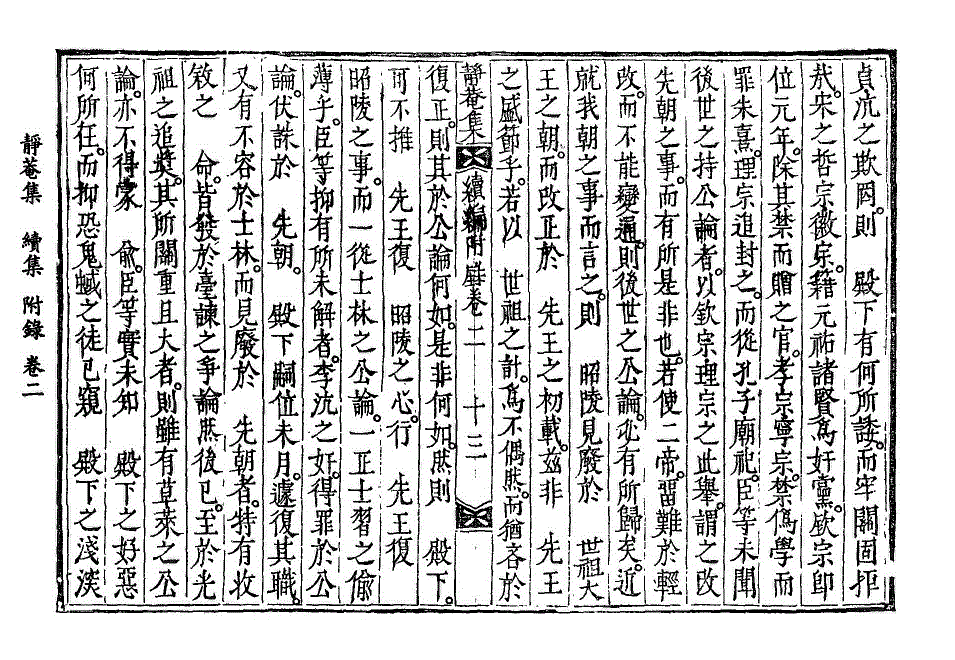 贞,沆之欺罔。则 殿下有何所诿。而牢关固拒哉。宋之哲宗,徽宗。籍元祐诸贤为奸党。钦宗即位元年。除其禁而赠之官。孝宗,宁宗。禁伪学而罪朱熹。理宗追封之。而从孔子庙祀。臣等未闻后世之持公论者。以钦宗,理宗之此举。谓之改先朝之事。而有所是非也。若使二帝。留难于轻改。而不能变通。则后世之公论。必有所归矣。近就我朝之事而言之。则 昭陵见废于 世祖大王之朝。而改正于 先王之初载。兹非 先王之盛节乎。若以 世祖之计。为不偶然。而犹吝于复正。则其于公论何如。是非何如。然则 殿下。可不推 先王复 昭陵之心。行 先王复 昭陵之事。而一从士林之公论。一正士习之偷薄乎。臣等抑有所未解者。李沆之奸。得罪于公论。伏诛于 先朝。 殿下嗣位未月。遽复其职。又有不容于士林。而见废于 先朝者。特有收叙之 命。皆发于台谏之争论然后已。至于光祖之追奖。其所关重且大者。则虽有草莱之公论。亦不得蒙 俞。臣等实未知 殿下之好恶何所在。而抑恐鬼蜮之徒已窥 殿下之浅深
贞,沆之欺罔。则 殿下有何所诿。而牢关固拒哉。宋之哲宗,徽宗。籍元祐诸贤为奸党。钦宗即位元年。除其禁而赠之官。孝宗,宁宗。禁伪学而罪朱熹。理宗追封之。而从孔子庙祀。臣等未闻后世之持公论者。以钦宗,理宗之此举。谓之改先朝之事。而有所是非也。若使二帝。留难于轻改。而不能变通。则后世之公论。必有所归矣。近就我朝之事而言之。则 昭陵见废于 世祖大王之朝。而改正于 先王之初载。兹非 先王之盛节乎。若以 世祖之计。为不偶然。而犹吝于复正。则其于公论何如。是非何如。然则 殿下。可不推 先王复 昭陵之心。行 先王复 昭陵之事。而一从士林之公论。一正士习之偷薄乎。臣等抑有所未解者。李沆之奸。得罪于公论。伏诛于 先朝。 殿下嗣位未月。遽复其职。又有不容于士林。而见废于 先朝者。特有收叙之 命。皆发于台谏之争论然后已。至于光祖之追奖。其所关重且大者。则虽有草莱之公论。亦不得蒙 俞。臣等实未知 殿下之好恶何所在。而抑恐鬼蜮之徒已窥 殿下之浅深静庵先生续集附录卷之二 第 1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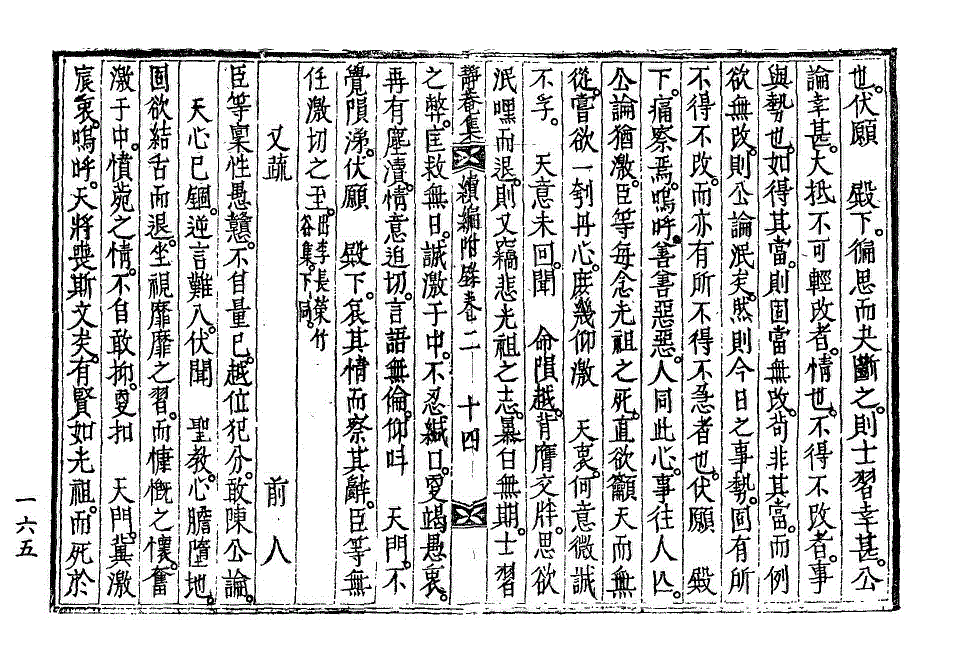 也。伏愿 殿下。遍思而夬断之。则士习幸甚。公论幸甚。大抵不可轻改者。情也。不得不改者。事与势也。如得其当。则固当无改。苟非其当。而例欲无改。则公论泯矣。然则今日之事势。固有所不得不改。而亦有所不得不急者也。伏愿 殿下。痛察焉。呜呼。善善恶恶。人同此心。事往人亡。公论犹激。臣等每念光祖之死。直欲吁天而无从。尝欲一刳丹心。庶几仰激 天衷。何意微诚不孚。 天意未回。闻 命陨越。背膺交牉。思欲泯嘿而退。则又窃悲光祖之志。暴白无期。士习之弊。匡救无日。诚激于中。不忍缄口。更竭愚衷。再有尘渎。情意迫切。言语无伦。仰叫 天门。不觉陨涕。伏愿 殿下。哀其情而察其辞。臣等无任激切之至。(出李长荣竹谷集。下同。)
也。伏愿 殿下。遍思而夬断之。则士习幸甚。公论幸甚。大抵不可轻改者。情也。不得不改者。事与势也。如得其当。则固当无改。苟非其当。而例欲无改。则公论泯矣。然则今日之事势。固有所不得不改。而亦有所不得不急者也。伏愿 殿下。痛察焉。呜呼。善善恶恶。人同此心。事往人亡。公论犹激。臣等每念光祖之死。直欲吁天而无从。尝欲一刳丹心。庶几仰激 天衷。何意微诚不孚。 天意未回。闻 命陨越。背膺交牉。思欲泯嘿而退。则又窃悲光祖之志。暴白无期。士习之弊。匡救无日。诚激于中。不忍缄口。更竭愚衷。再有尘渎。情意迫切。言语无伦。仰叫 天门。不觉陨涕。伏愿 殿下。哀其情而察其辞。臣等无任激切之至。(出李长荣竹谷集。下同。)伸冤疏(李长荣)
臣等禀性愚戆。不自量已。越位犯分。敢陈公论。 天心已锢。逆言难入。伏闻 圣教。心胆堕地。固欲结舌而退。坐视靡靡之习。而慵慨之怀。奋激于中。愤菀之情。不自敢抑。更扣 天门。冀激宸衷。呜呼。天将丧斯文矣。有贤如光祖。而死于
静庵先生续集附录卷之二 第 166H 页
 诬枉。得君如 殿下。而公论不行。臣等伏地痛心。不知 天心之终何如也。呜呼。道其坠地矣。一光祖死。而举世吹薤。危言危行。为世大禁。于今十数年。是非犹不能明。臣等仰天疾首。不知士习之终何如也。呜呼。谗谄面谀之人。至矣。好恶既分。贤邪类至。故訑訑之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今我 殿下。复奸人之职。犹恐不及。申贤者之枉。苟有所诿。消长之机。于斯判矣。臣等伤今思古。不知国脉之终何如也。然则 殿下之好恶。可知矣。公论不行。是非不明。正学一脉。湮灭无馀。臣等私忧过计。窃不胜漆室嫠妇之忧。未尝不流涕于士习。痛哭于国脉也。噫。命之穷矣。亦已矣。言有尽而情则无穷。事已往而公论难泯。略陈一得之愚虑。庶几白日之昭临。伏愿 殿下。赦其狂妄。而矜其愚衷。情激意迫。矢口尽言。吞声饮泣。伏纸陨越。臣等无任迫切之至。谨昧死以闻。
诬枉。得君如 殿下。而公论不行。臣等伏地痛心。不知 天心之终何如也。呜呼。道其坠地矣。一光祖死。而举世吹薤。危言危行。为世大禁。于今十数年。是非犹不能明。臣等仰天疾首。不知士习之终何如也。呜呼。谗谄面谀之人。至矣。好恶既分。贤邪类至。故訑訑之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今我 殿下。复奸人之职。犹恐不及。申贤者之枉。苟有所诿。消长之机。于斯判矣。臣等伤今思古。不知国脉之终何如也。然则 殿下之好恶。可知矣。公论不行。是非不明。正学一脉。湮灭无馀。臣等私忧过计。窃不胜漆室嫠妇之忧。未尝不流涕于士习。痛哭于国脉也。噫。命之穷矣。亦已矣。言有尽而情则无穷。事已往而公论难泯。略陈一得之愚虑。庶几白日之昭临。伏愿 殿下。赦其狂妄。而矜其愚衷。情激意迫。矢口尽言。吞声饮泣。伏纸陨越。臣等无任迫切之至。谨昧死以闻。据竹谷集。有三疏。初疏即附录所载。康惟善疏也。盖公在太学。与康公联名。岂康公居首。而草疏在公耶。公与人书有曰。十三日。与馆
静庵先生续集附录卷之二 第 1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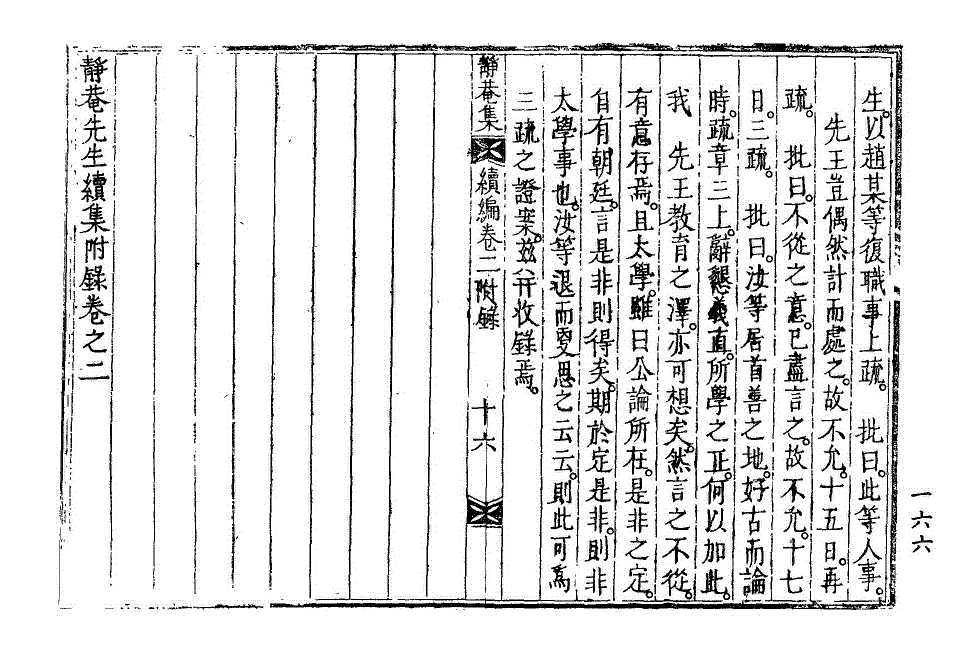 生。以赵某等复职事上疏。 批曰。此等人事。 先王岂偶然计而处之。故不允。十五日。再疏。 批曰。不从之意。已尽言之。故不允。十七日。三疏。 批曰。汝等居首善之地。好古而论时。疏章三上。辞恳义直。所学之正。何以加此。我 先王教育之泽。亦可想矣。然言之不从。有意存焉。且太学。虽曰公论所在。是非之定。自有朝廷。言是非则得矣。期于定是非。则非太学事也。汝等退而更思之云云。则此可为三疏之證案。兹并收录焉。
生。以赵某等复职事上疏。 批曰。此等人事。 先王岂偶然计而处之。故不允。十五日。再疏。 批曰。不从之意。已尽言之。故不允。十七日。三疏。 批曰。汝等居首善之地。好古而论时。疏章三上。辞恳义直。所学之正。何以加此。我 先王教育之泽。亦可想矣。然言之不从。有意存焉。且太学。虽曰公论所在。是非之定。自有朝廷。言是非则得矣。期于定是非。则非太学事也。汝等退而更思之云云。则此可为三疏之證案。兹并收录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