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卷三十四 第 1a 页 WYG0209-0710c.png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四书讲义困勉录卷三十四
赠内阁学士陆陇其撰
告子上
性犹𣏌柳也章总旨 李衷一曰据告子以人性为仁
义之说何尝以仁义为不可为也彼其意但谓非人
性中本有必为之而后成耳 张彦陵曰孟子就他
为字生出戕贼字来见他说得大有破绽
性犹𣏌柳也节 张彦陵曰性犹𣏌柳二句虚至下二
卷三十四 第 1b 页 WYG0209-0710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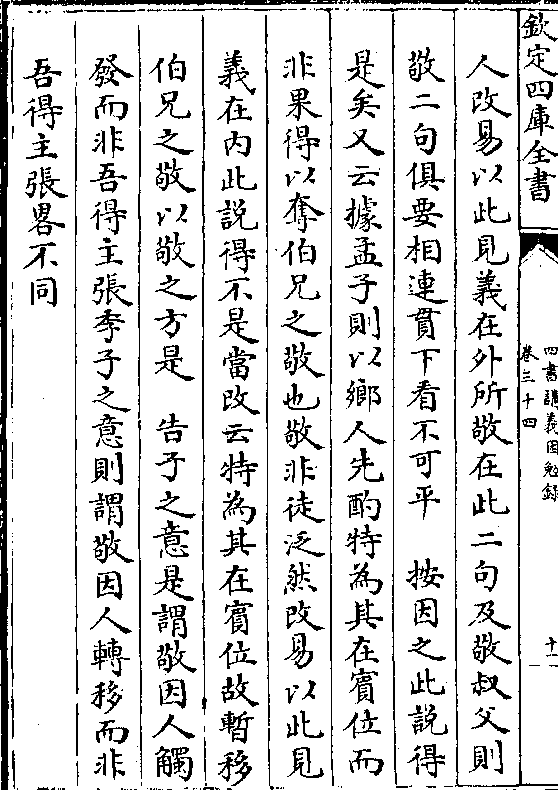 句方可见人性本无仁义意且其言性亦即生之谓
句方可见人性本无仁义意且其言性亦即生之谓性也不可用降衷秉彝等语 𣏌柳杯棬蒙引亦说
得未明然大概𣏌柳是一物而杯棬是两物 吴因
之曰告子认性为气认仁义为理认性在有生之前
认仁义在有生之后是把性与仁义分作两项看了
故有以人性为仁义之说
子能顺𣏌柳之性节 吴因之曰此段虽未言性善然
卷三十四 第 2a 页 WYG0209-0711a.png
 谓之不可戕贼则性善亦隐然在言外矣 孟子辟
谓之不可戕贼则性善亦隐然在言外矣 孟子辟告子不说性如何善者盖孟子性善之论必告子所
素闻但他欲以自已议论破孟子之说故孟子只辟
其说之非而性善不待言矣 翼注曰子能二句非
两问之辞乃是言此岂能如彼必将如此也是决词
附四书脉曰子能二句本决辞却像商量言你还
是顺其性而为之是逆其性而为之其待戕贼必矣
勿于能上加岂字将上加必字 贡受轩曰告子言
性原有何仁义如𣏌柳本无杯棬孟子言何不将他
卷三十四 第 2b 页 WYG0209-0711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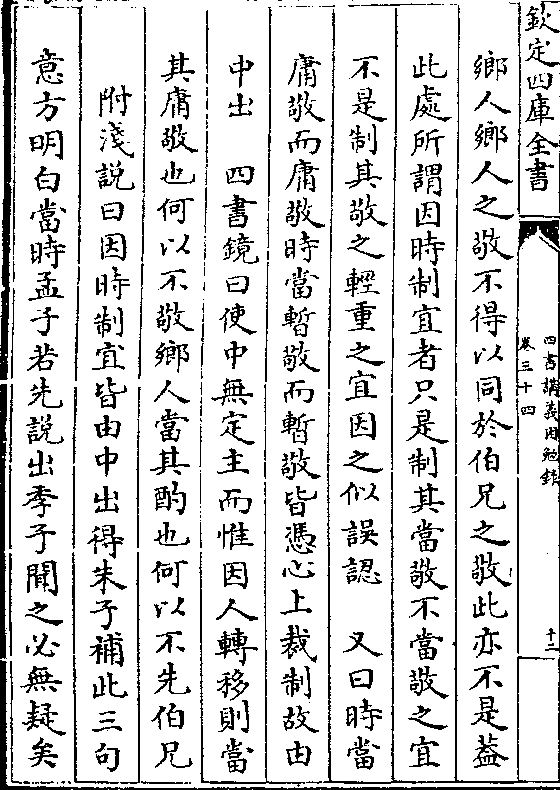 木做杯棬只缘𣏌柳之性原有杯棬故顺其性而成
木做杯棬只缘𣏌柳之性原有杯棬故顺其性而成之耳若本无杯棬而人为加之是戕贼其性也如牛
性本耕犬性本守马性本乘皆因其性而付以此事
性中原有仁义因其机而扩充之非祸性也 祸仁
义翼注又载一说曰以仁义为祸性也背注不可从
吴因之曰此篇言性多端然可一言以蔽曰性即
仁义有善无恶固缘情可验而圣凡一致者也然性
卷三十四 第 3a 页 WYG0209-0711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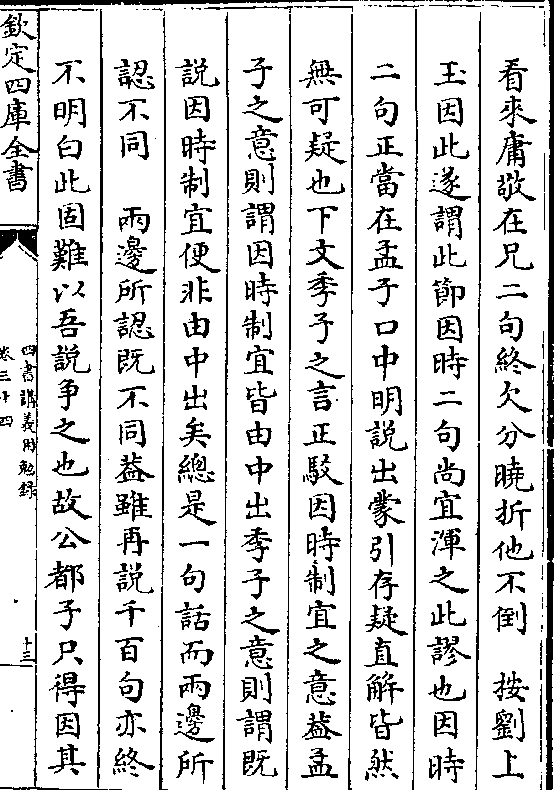 本善不可无察识扩充之功故继之以人心得养失
本善不可无察识扩充之功故继之以人心得养失养之分齐王一暴十寒之喻究竟于舍生取义之真
反覆乎宫室妻妾外诱之惑辨析乎养其大体小体
之孰重孰轻无非归之实践履以全其在我而已孟
子一生学问一生莫大之功全在性善之论盖性既
善则父可使之慈子可使之孝为君者可使法尧为
臣者可使法舜然后天地以位人极以立不然则相
糜相刃弑父弑君无所不至而曰性本恶也奈之何
哉 又曰告子𣏌柳食色生之谓性诸章是故意设
卷三十四 第 3b 页 WYG0209-0711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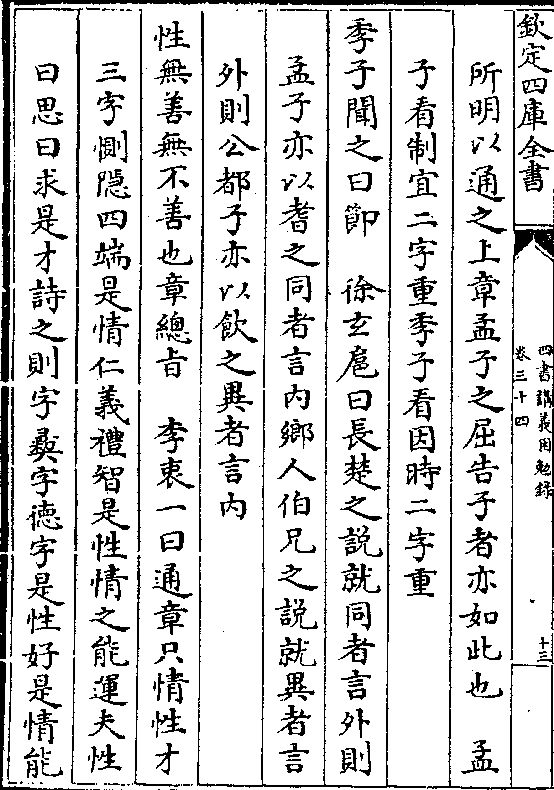 为此等议论要与孟子抗衡讲中要体会此意 又
为此等议论要与孟子抗衡讲中要体会此意 又曰𣏌柳章只辨得一为字湍水章只辨得一决字盖
搏击节正在决字生议论也白之谓白章只辨得一
生字白马白人两章只辨得一义外字
性犹湍水也章总旨 吴因之曰看告子立论处全要
模想性无定体意看孟子辟他处全要模想性有定
体意
卷三十四 第 4a 页 WYG0209-0712a.png
 性犹湍水也节 按性本定于善则不待决矣其不善
性犹湍水也节 按性本定于善则不待决矣其不善则必待决也搏激者决之谓也
水信无分于东西节 张彦陵曰孟子以上下字换他
东西字便明 翼注曰人性之善也四句似叠床盖
下二句决上二句之意无有不是决词不重同意
今夫水节 张彦陵曰此节不是为不善人分疏正见
人无有不善处水之过颡在山由于搏击来则水之
无有不下也明矣为不善而出于使可见天下即有
为不善之人决无有不善之性
卷三十四 第 4b 页 WYG0209-0712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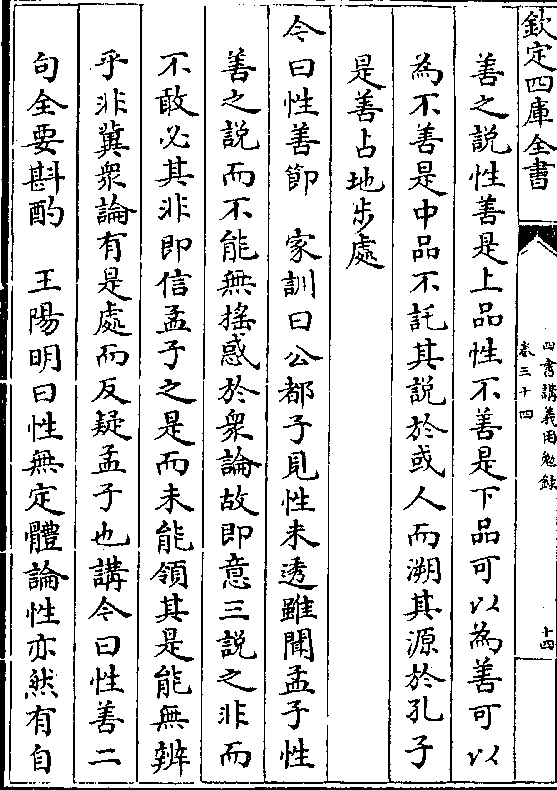 生之谓性章总旨 沈无回曰生之谓性告子亦未尝
生之谓性章总旨 沈无回曰生之谓性告子亦未尝不是只是见得统儱了不能柝到人之所以异于禽
兽者几希处故孟子以犬牛之性折之便无可解
生之谓性节 孟子以生之理为性则非徒人物之性
不同也且人物之生先不同矣告子只以生为性则
人物之生初无异也而人物之性亦不得谓有异矣
既以生为性则便不得复分人物此是一病非二
卷三十四 第 5a 页 WYG0209-0712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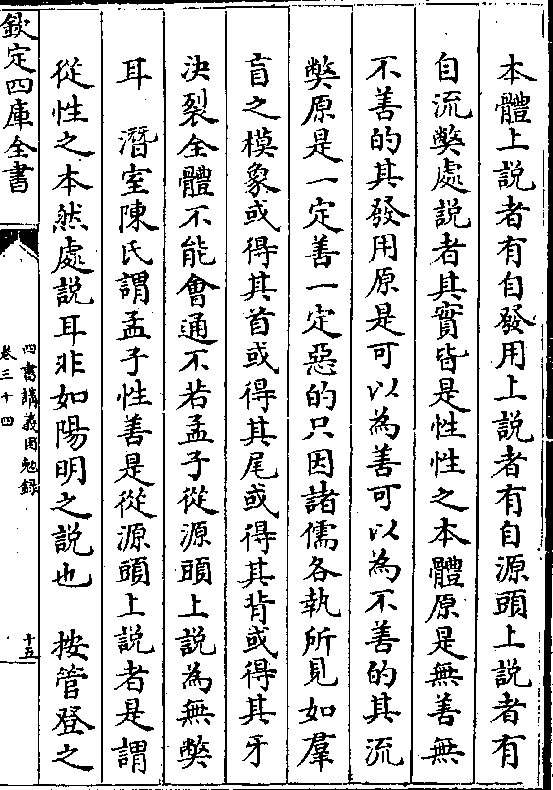 病也 蒙引双峰俱云知觉属心运动属身然则凡
病也 蒙引双峰俱云知觉属心运动属身然则凡知处皆属心凡行处皆属身矣与大学圣经知行之
分又不同盖亦可互相发也
生之谓性也两节 翼注曰白之谓白是凡物之白者
同谓之白则羽雪玉已该在内了孟子恐告子遁词
故再问以实之 吴因之曰白羽及白雪白玉各二
字连珠不必以上白字作称许看 直解曰告子之
言是徒泥其色之同而不思其质之异 第二节注
凡有生者同是一性句即贴本节似不妨蒙引谓此
卷三十四 第 5b 页 WYG0209-0712d.png
 处不当照注贴似拘误录 管登之曰读告子篇当
处不当照注贴似拘误录 管登之曰读告子篇当知生之谓性一句此告子论性之宗旨也𣏌柳之喻
本于此湍水之喻本于此食色仁内义外之论亦本
于此未尝少变其说 玩后面告子曰性无善无不
善也集注曰此即生之谓性食色性也之意至或曰
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集注曰此即湍水之说然
则告子此章虽是发明𣏌柳湍水二章之本旨然较
卷三十四 第 6a 页 WYG0209-0713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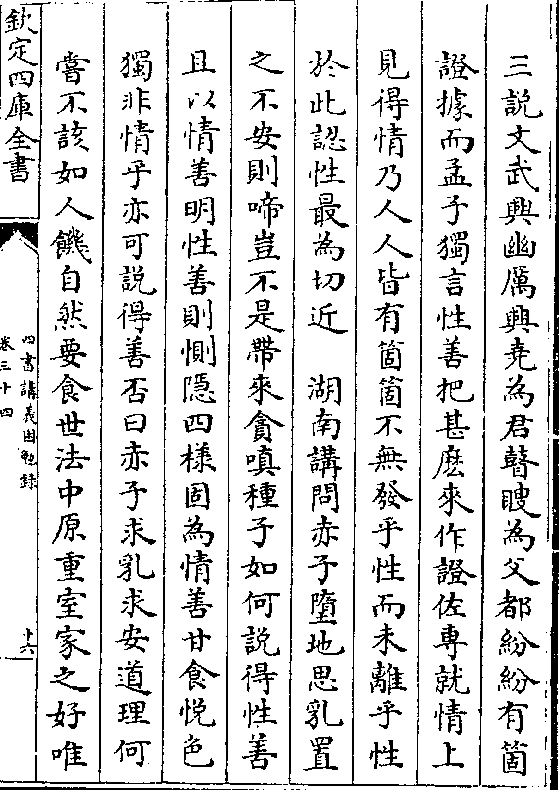 之𣏌柳湍水之说又稍变乎曰不然无善无不善之
之𣏌柳湍水之说又稍变乎曰不然无善无不善之说又在其后变出不必云说生之谓性时即变出(丁巳)
(十月十六改)
食色性也章总旨 吴因之曰此章是论仁义不是论
性 愚意论仁义正所以论性
食色性也节 告子之说虽屡变而生之谓性食色性
也之说乃其宗旨未尝变者也无善无不善之说乃
其定论终不变者也今乃曰仁内也非外也仁既在
内则性为有善而食色不可谓性矣曰非也告子所
卷三十四 第 6b 页 WYG0209-0713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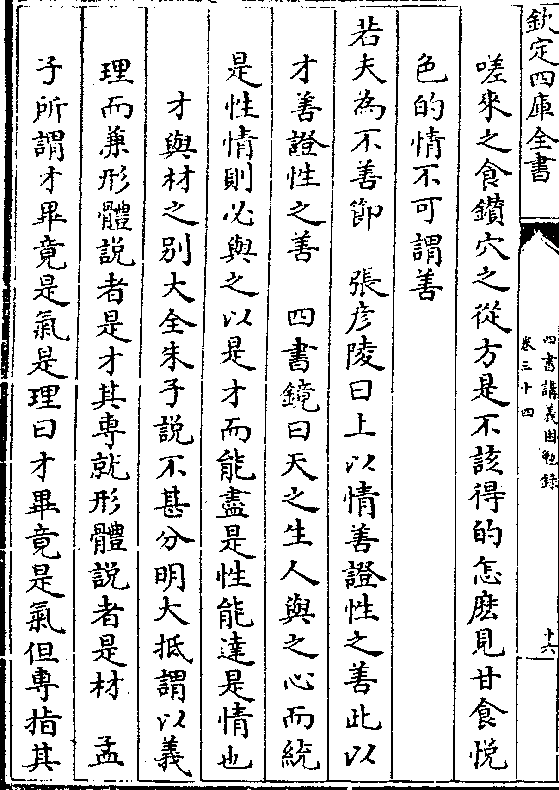 谓仁亦即指甘食悦色之类耳故其始以仁义为皆
谓仁亦即指甘食悦色之类耳故其始以仁义为皆外此则乂以仁为在内盖前之所谓仁乃指吾儒所
谓仁故以为在外此所谓仁乃告子所见为仁故以
为在内则其前后之旨固一也朱子谓告子得孟子
说方略认仁为在内恐未是集注亦无此意 朱子
谓告子亦不以仁为性之所有但比义差在内耳亦
恐未是盖谓之内则是指为性矣 仁者心之德爱
卷三十四 第 7a 页 WYG0209-0713c.png
 之理蒙引谓告子只说得心之爱德字理字都无了
之理蒙引谓告子只说得心之爱德字理字都无了固是矣又其所谓爱者亦只是爱食色之爱与夫爱
亲之爱耳若夫仁民爱物统体之爱又不在内矣
果如告子之说则物则非性而物欲是性矣道心非
性而人心是性矣 李毅侯曰告子食色谓性即生
之谓性之意其意谓食色是性何尝有仁义带来除
是仁还在内若义却断然在外了看来仁内二字亦
说得不分晓亦未见是但义外之说尤谬故曰何以
谓仁内而义独外也以折之旧解仁内四句根食色
卷三十四 第 7b 页 WYG0209-0713d.png
 性也来食为我心所甘色为我心所悦故曰仁爱之
性也来食为我心所甘色为我心所悦故曰仁爱之心生于内食之所在宜甘色之所在宜悦故曰事物
之宜由于外支离难解 按此即朱子略认仁为在
内之说(癸卯十一月初八) 因之又曰告子言仁内义外是
仁纵在内义终不在内也 按此即朱子略认仁为
在内之说也不似告子口气 朱子略认仁为在内
亦不以仁为性之所有其说甚是余初不取似不是
卷三十四 第 8a 页 WYG0209-0714a.png
 姑识以俟再定(癸卯十一月初七) 四书镜曰告子意以凡
姑识以俟再定(癸卯十一月初七) 四书镜曰告子意以凡出于中心所欲不因外而生者是之谓仁在内凡事
宜在外而强我以从者是之谓义在外二句不拘食
色亦不离食色 吴因之曰义本是心之制事之宜
告子遗却心之制只言事之宜且所谓宜又全据事
物现成者言更不及处合其宜之意 沈无回曰义
外亦不专以敬长言即仁中许多条件不从孩提之
性生来者便属义
何以谓仁内义外也节 四书脉曰何以谓仁在内而
卷三十四 第 8b 页 WYG0209-0714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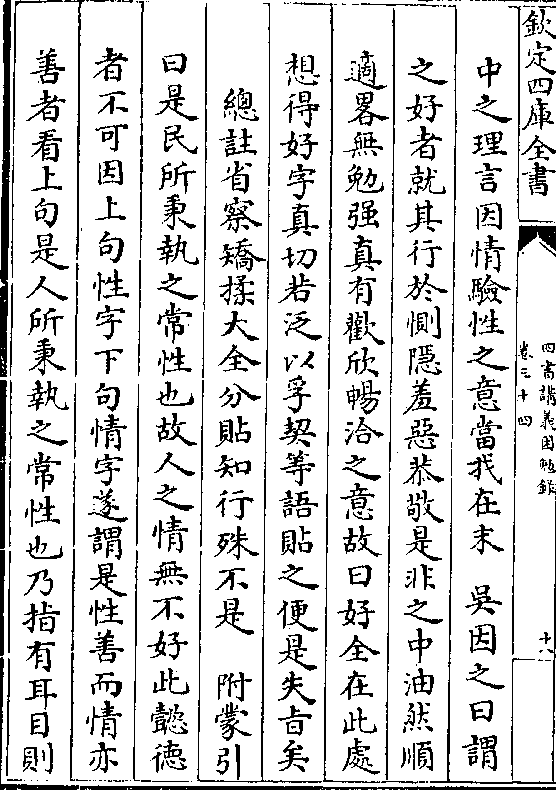 义独在外重辟义外边 翼注曰我长之且只说以
义独在外重辟义外边 翼注曰我长之且只说以彼为长勿露敬字直至长人之长方可露敬字 又
曰故谓之外也指义言遥承上长长非近接白白也
异于白马之白也节 吴因之曰通节口气顺递说下
而存疑诸书作两段意可怪 翼注曰白马之白下
白字是白色上白字是称谓馀仿此 吴因之曰白
马二句甚轻只起下 张彦陵曰白马四句不是空
卷三十四 第 9a 页 WYG0209-0714c.png
 空辟其以白喻长之非全要借长马长人别出长之
空辟其以白喻长之非全要借长马长人别出长之在我破他非有长于我之说 白马四句是辟其以
白喻长之非以白喻长所以为非者盖白马白人无
异而长马长人则必区别于人与马之际其权度悉
由中出便可见义之非外所以以白喻长为非也须
发得此意透盖辟其以白喻长之非即是辟其外义
之非也 附吴因之曰不识长马之长无以异于长
人之长正与非有长于我对且谓二句正与故谓之
外对 依蒙引存疑则不识二句已兼与故谓之外
卷三十四 第 9b 页 WYG0209-0714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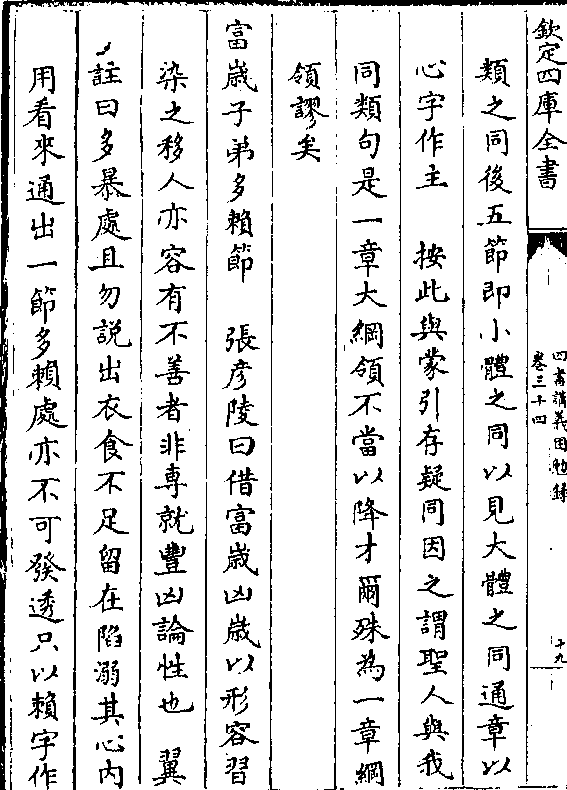 对 四书镜曰且谓二句两乎字须实断义之非外
对 四书镜曰且谓二句两乎字须实断义之非外且谓长者义乎二句言我不必问义之内外而且
问子以何者为义知何者之为义则其内外不待辨
矣与白马四句毕竟是两层 问且谓长者二句告
子何以不答也曰告子意以为义虽长之者而不在
长者然长之之心原起于外则义仍在外矣且谓二
句固不必答矣 盖告子亦是以长之者为义但究
卷三十四 第 10a 页 WYG0209-0715a.png
 其实则是认长者为义矣
其实则是认长者为义矣吾弟则爱之节 告子见孟子以长马长人之不同證
义之非外因以长楚长长吾长證义之外 孟子白
马四句先说长之之心在内故说长之者为义便见
义之在内告子长楚长一段乃说长之之心在外则
虽以长之者为义而义仍在外矣故人谓此章得力
在长之者一句吾谓此句非得力之处也
耆秦人之炙节 莫中江曰虽借耆炙喻长长其实嗜
亦从爱来见义若说外则仁亦说得外今既明于仁
卷三十四 第 10b 页 WYG0209-0715b.png
 内则亦可以即此明彼矣 翼注曰物字指炙然字
内则亦可以即此明彼矣 翼注曰物字指炙然字指嗜之同 章末须缴云义既非外则仁益非外仁
义非外则性固善而食色不可为性矣
何以谓义内也两节 吴因之曰行吾敬吾字极重后
孟季子两执己见只是要破坏吾字孟子公都子各
伸其说只是要阐明吾字盖说个在吾则义内说个
在人则义外论义大关键正在此 按重吾字极是
卷三十四 第 11a 页 WYG0209-0715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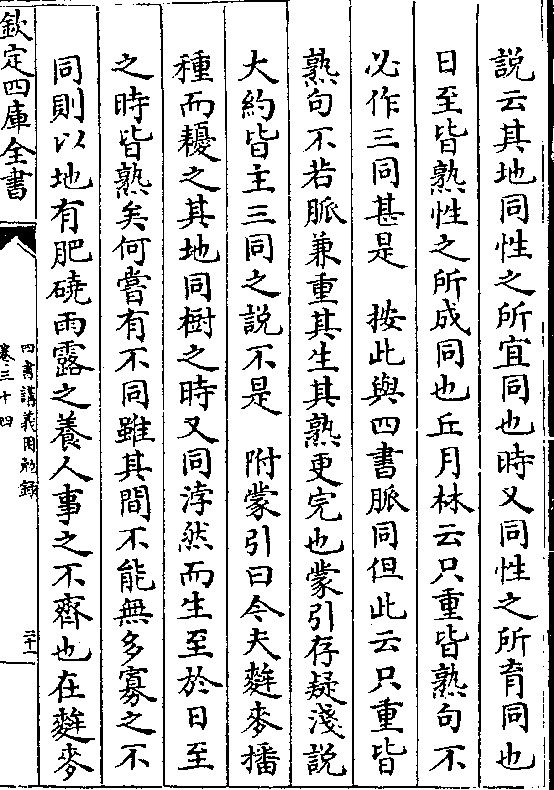 下文因时制宜之意虽重然亦归到吾字上盖谓因
下文因时制宜之意虽重然亦归到吾字上盖谓因时制宜亦是吾也所谓皆由中出也 吴因之曰公
都子行吾敬之言虽已得其意然至于不能答毕竟
是认吾不透 盖但知敬由于吾而不知因时制宜
之敬亦由于吾也
乡人长于伯兄一岁节 吴因之曰此与下节俱把乡
人伯兄并言然辨难激切处都在乡人一边据季子
则以敬在伯兄矣而乡人之酌乃有以移夺之敬因
人改易以此见义在外所敬在此二句及敬叔父则
卷三十四 第 11b 页 WYG0209-0715d.png
 敬二句俱要相连贯下看不可平 按因之此说得
敬二句俱要相连贯下看不可平 按因之此说得是矣又云据孟子则以乡人先酌特为其在宾位而
非果得以夺伯兄之敬也敬非徒泛然改易以此见
义在内此说得不是当改云特为其在宾位故暂移
伯兄之敬以敬之方是 告子之意是谓敬因人触
发而非吾得主张季子之意则谓敬因人转移而非
吾得主张略不同
卷三十四 第 12a 页 WYG0209-0716a.png
 公都子不能答节 吴因之曰彼将曰在位故也虽指
公都子不能答节 吴因之曰彼将曰在位故也虽指弟言却要归到叔父上见弟若不在尸位叔父之敬
岂有时易乎子亦曰在位故也虽指乡人言亦要归
到伯兄上见乡人若不在宾位伯兄之敬岂有时易
乎庸敬斯须随时斟酌所敬所长非胸中漫无主张
而徒因人转移者也义之在内昭昭矣 翼注曰前
一在位指弟在尸位后一在位指乡人在宾客之位
吴因之曰庸敬在兄二句见伯兄之敬未尝同于
乡人乡人之敬不得以同于伯兄之敬此亦不是盖
卷三十四 第 12b 页 WYG0209-0716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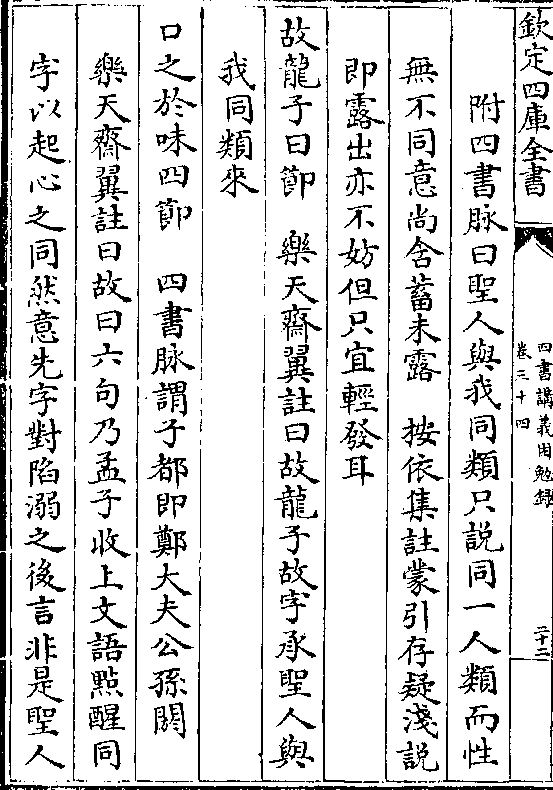 此处所谓因时制宜者只是制其当敬不当敬之宜
此处所谓因时制宜者只是制其当敬不当敬之宜不是制其敬之轻重之宜因之似误认 又曰时当
庸敬而庸敬时当暂敬而暂敬皆凭心上裁制故由
中出 四书镜曰使中无定主而惟因人转移则当
其庸敬也何以不敬乡人当其酌也何以不先伯兄
附浅说曰因时制宜皆由中出得朱子补此三句
意方明白当时孟子若先说出季子闻之必无疑矣
卷三十四 第 13a 页 WYG0209-0716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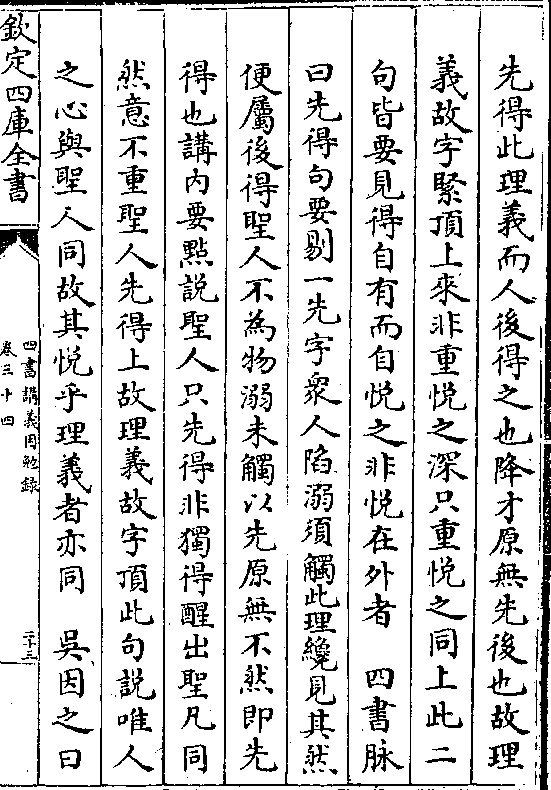 看来庸敬在兄二句终欠分晓折他不倒 按刘上
看来庸敬在兄二句终欠分晓折他不倒 按刘上玉因此遂谓此节因时二句尚宜浑之此谬也因时
二句正当在孟子口中明说出蒙引存疑直解皆然
无可疑也下文季子之言正驳因时制宜之意盖孟
子之意则谓因时制宜皆由中出季子之意则谓既
说因时制宜便非由中出矣总是一句话而两边所
认不同 两边所认既不同盖虽再说千百句亦终
不明白此固难以吾说争之也故公都子只得因其
所明以通之上章孟子之屈告子者亦如此也 孟
卷三十四 第 13b 页 WYG0209-0716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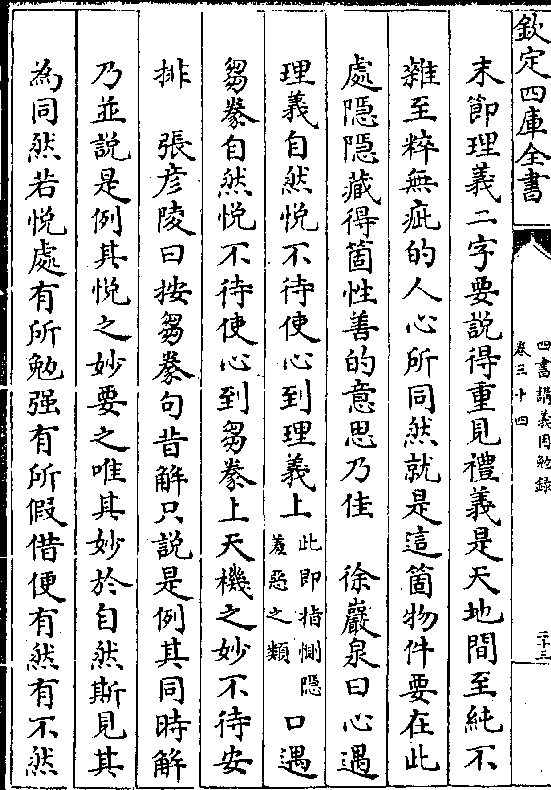 子看制宜二字重季子看因时二字重
子看制宜二字重季子看因时二字重季子闻之曰节 徐玄扈曰长楚之说就同者言外则
孟子亦以耆之同者言内乡人伯兄之说就异者言
外则公都子亦以饮之异者言内
性无善无不善也章总旨 李衷一曰通章只情性才
三字恻隐四端是情仁义礼智是性情之能运夫性
曰思曰求是才诗之则字彝字德字是性好是情能
卷三十四 第 14a 页 WYG0209-0717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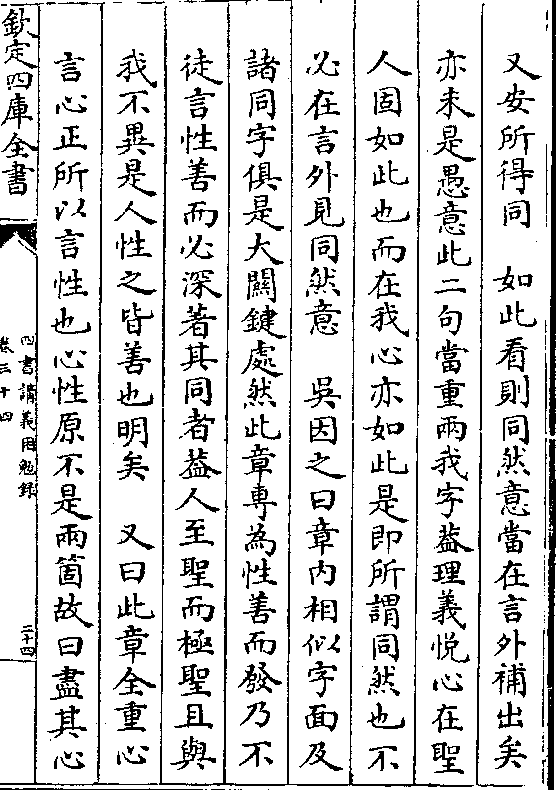 好是懿德是才孔颍达曰性情才三者合而言之则
好是懿德是才孔颍达曰性情才三者合而言之则一物也分而言之则有三名 张彦陵曰引诗处提
出一天字即天命之谓性之说并性善源头指出
性无善无不善也三节 翼注曰三说一言性之浑沦
一言性之无定一言性之有定 吴淯世咏思评韩
文公原性曰三品之说即孔子上智下愚性近习远
之说上智是上品下愚是下品性近习远是中品又
即兼告子内有性善有性不善可以为善可以为不
善之说性善是上品性不善是下品可以为善可以
卷三十四 第 14b 页 WYG0209-0717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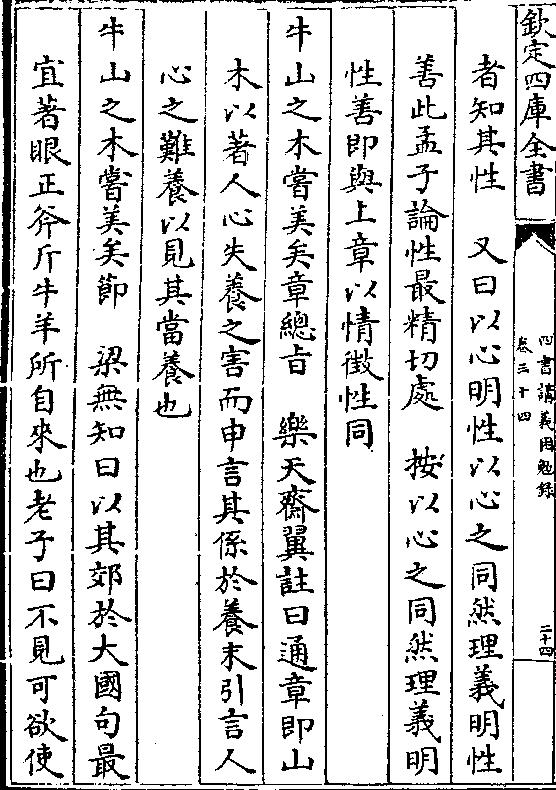 为不善是中品不托其说于或人而溯其源于孔子
为不善是中品不托其说于或人而溯其源于孔子是善占地步处
今曰性善节 家训曰公都子见性未透虽闻孟子性
善之说而不能无摇惑于众论故即意三说之非而
不敢必其非即信孟子之是而未能领其是能无辨
乎非冀众论有是处而反疑孟子也讲今曰性善二
句全要斟酌 王阳明曰性无定体论性亦然有自
卷三十四 第 15a 页 WYG0209-0717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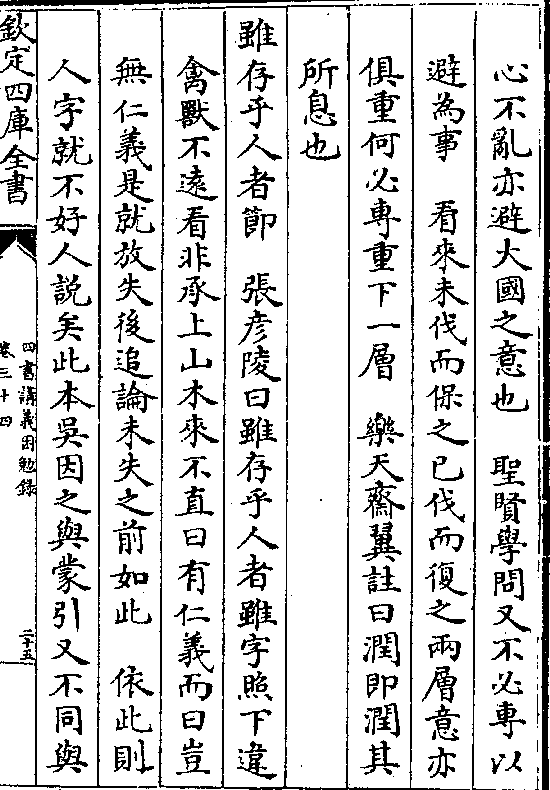 本体上说者有自发用上说者有自源头上说者有
本体上说者有自发用上说者有自源头上说者有自流弊处说者其实皆是性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
不善的其发用原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其流
弊原是一定善一定恶的只因诸儒各执所见如群
盲之模象或得其首或得其尾或得其背或得其牙
决裂全体不能会通不若孟子从源头上说为无弊
耳 潜室陈氏谓孟子性善是从源头上说者是谓
从性之本然处说耳非如阳明之说也 按管登之
又谓孔子以相近言性是从人生而静时说孟子以
卷三十四 第 15b 页 WYG0209-0717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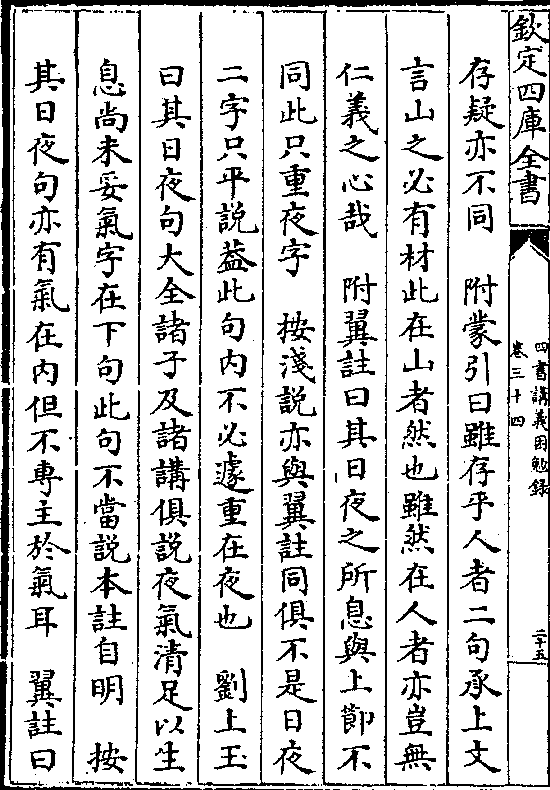 继善言性则从人生而静以上说也此即阳明之说
继善言性则从人生而静以上说也此即阳明之说非孟子本旨也观双峰云人未生以前不唤做性可
见
乃若其情节 乃若二字要见孟子一段确有證据光
景不是勉强等一證(丁巳十一月) 其情其字集注蒙引
存疑浅说皆指人言乐天斋翼注谓指性言恐不是
湖南讲曰性原是无声臭的随人体认故有纷纷
卷三十四 第 16a 页 WYG0209-0718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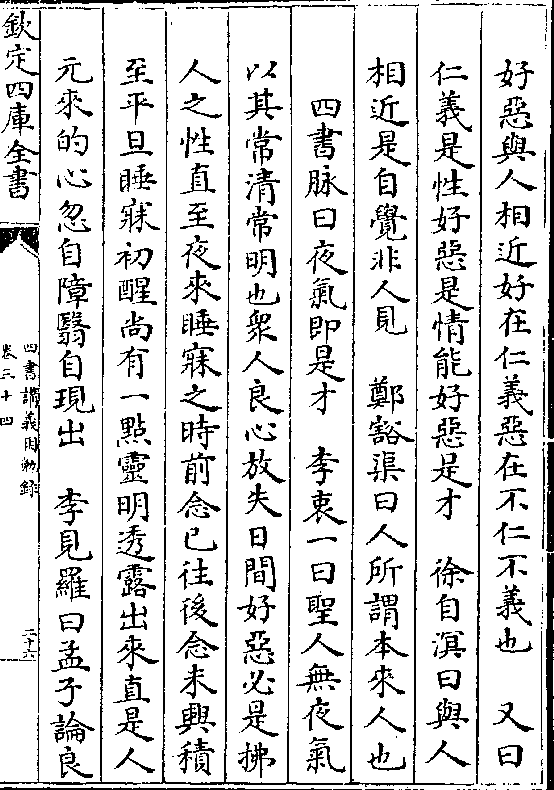 三说文武兴幽厉兴尧为君瞽瞍为父都纷纷有个
三说文武兴幽厉兴尧为君瞽瞍为父都纷纷有个證据而孟子独言性善把甚么来作證佐专就情上
见得情乃人人皆有个个不无发乎性而未离乎性
于此认性最为切近 湖南讲问赤子堕地思乳置
之不安则啼岂不是带来贪嗔种子如何说得性善
且以情善明性善则恻隐四样固为情善甘食悦色
独非情乎亦可说得善否曰赤子求乳求安道理何
尝不该如人饥自然要食世法中原重室家之好唯
嗟来之食钻穴之从方是不该得的怎么见甘食悦
卷三十四 第 16b 页 WYG0209-0718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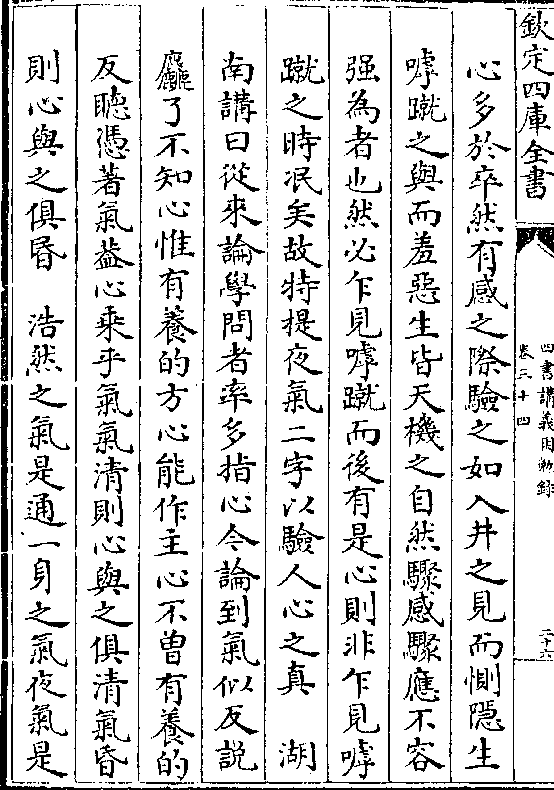 色的情不可谓善
色的情不可谓善若夫为不善节 张彦陵曰上以情善證性之善此以
才善證性之善 四书镜曰天之生人与之心而统
是性情则必与之以是才而能尽是性能达是情也
才与材之别大全朱子说不甚分明大抵谓以义
理而兼形体说者是才其专就形体说者是材 孟
子所谓才毕竟是气是理曰才毕竟是气但专指其
卷三十四 第 17a 页 WYG0209-0718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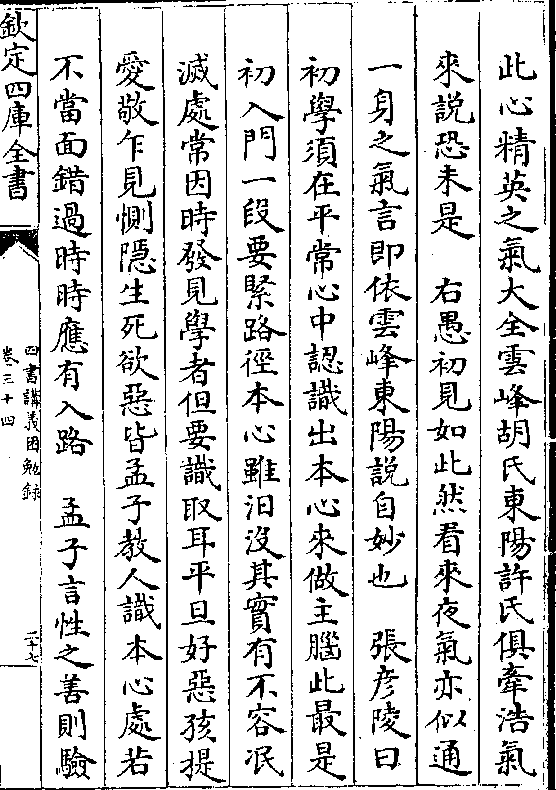 自理而发者故集注曰孟子专指其发于性者言之
自理而发者故集注曰孟子专指其发于性者言之存疑亦曰孟子言才自理言也愚意此所谓才即是
浩然之气但才则兼知行在内耳又志亦在其内
双峰以良能来解才字蒙引谓其最切是矣然愚意
更欲兼良知说
恻隐之心节 附存疑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四句是
解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恻隐之心仁也至我固有
之也是解乃所谓善弗思耳矣至不能尽其才是解
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 按存疑段落与新安陈氏
卷三十四 第 17b 页 WYG0209-0718d.png
 同与浅说达说大同小异浅说达说得之 吴因之
同与浅说达说大同小异浅说达说得之 吴因之曰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三句与不能尽其才紧相接
应盖谓之曰我固有者见我要仁便能仁我要义便
能义我要礼智便能礼智此处正是个才善的意思
若先说固有后方补出才善便非本旨 四书脉曰
仁义礼智三句还带下说以起弗思句 乐天斋翼
注曰烁字要体自外至内意言四者虽因情始见非
卷三十四 第 18a 页 WYG0209-0719a.png
 缘情后有非如火之销金自外而入也二句一反一
缘情后有非如火之销金自外而入也二句一反一正 四书脉曰得谓得其恻隐等之善 翼注曰或
相倍蓰句主舍则失之去求则得之者之远言下句
方接得 吴因之曰我有才无奈不肯求尽其才二
句道尽下半节大旨
天生蒸民节 张彦陵曰情才性前已发明此节只重
引孔子赞的诗词揭出一个真證佐 又曰蒸民便
是圣凡无两样 乐天斋翼注曰物以形言则以形
中之理言因情验性之意当我在末 吴因之曰谓
卷三十四 第 18b 页 WYG0209-0719b.png
 之好者就其行于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中油然顺
之好者就其行于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中油然顺适略无勉强真有欢欣畅洽之意故曰好全在此处
想得好字真切若泛以孚契等语贴之便是失旨矣
总注省察矫揉大全分贴知行殊不是 附蒙引
曰是民所秉执之常性也故人之情无不好此懿德
者不可因上句性字下句情字遂谓是性善而情亦
善者看上句是人所秉执之常性也乃指有耳目则
卷三十四 第 19a 页 WYG0209-0719c.png
 有聪明之德有父子则有慈孝之心似亦为情矣上
有聪明之德有父子则有慈孝之心似亦为情矣上文则字即是 按蒙引此条背注不可从大全浅说
达说俱不如此说看来此处所谓聪明之德慈孝之
心似俱当于性上说诸儒论性不同非是于善恶上
不明乃性字安顿不着
富岁子弟多赖章总旨 翼注曰首节非天之降才尔
殊也一句是主下面同类同嗜同听同美同然皆自
非殊字生出首节是纲次二节即物类之同以见人
类之同后五节即小体之同以见大体之同通章以
卷三十四 第 19b 页 WYG0209-0719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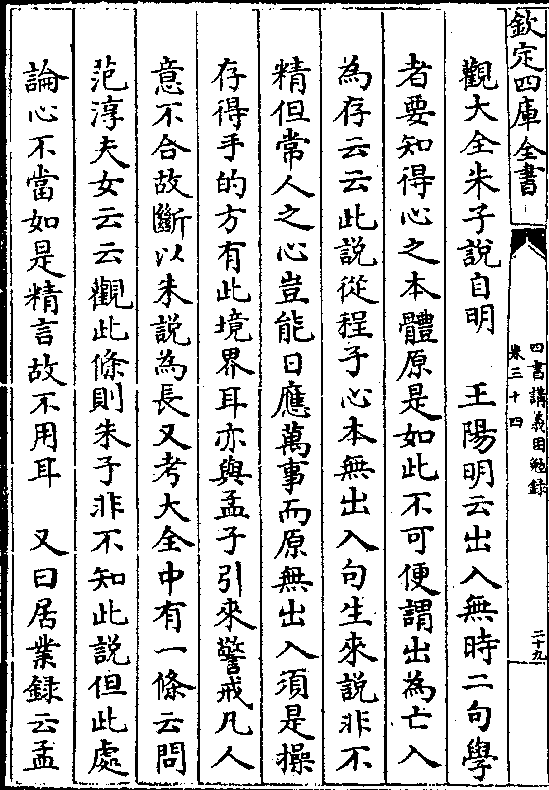 心字作主 按此与蒙引存疑同因之谓圣人与我
心字作主 按此与蒙引存疑同因之谓圣人与我同类句是一章大纲领不当以降才尔殊为一章纲
领谬矣
富岁子弟多赖节 张彦陵曰借富岁凶岁以形容习
染之移人亦容有不善者非专就丰凶论性也 翼
注曰多暴处且勿说出衣食不足留在陷溺其心内
用看来通出一节多赖处亦不可发透只以赖字作
卷三十四 第 20a 页 WYG0209-0720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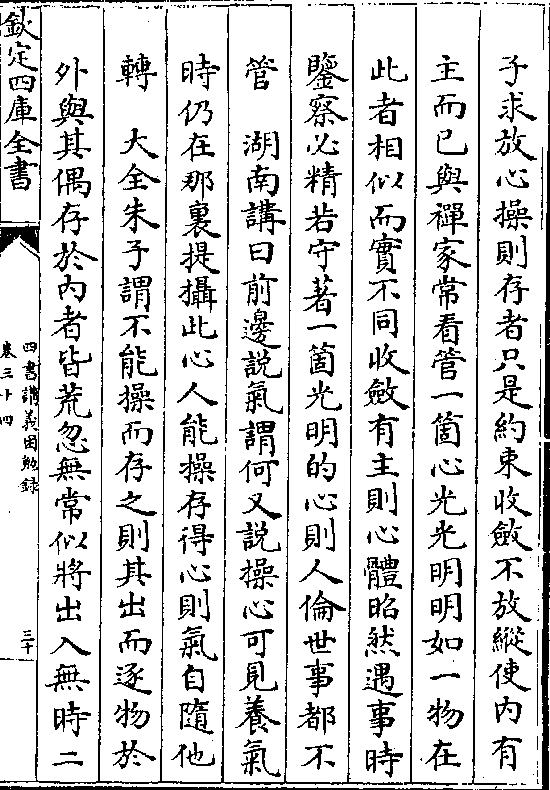 善字说过如人暴横者谓之无赖或云无藉即此赖
善字说过如人暴横者谓之无赖或云无藉即此赖字意 多暴即是非僻之心生不必说到事为而后
为暴也此处文势与苟无恒心放僻邪侈略异存疑
殊混 若陷溺其心与非僻之心生则仍是两层也
蒙引谓不曰降性降情而独曰才者就所为上为
切依此则才专就发处见依前章四书镜之说则才
兼就性情上说兼说为是但此章大旨则在发处说
耳 徐儆弦曰饥寒疾苦之迫其身其为陷溺也浅
纷华靡丽之荡其心其为陷溺也深此又不可以多
卷三十四 第 20b 页 WYG0209-0720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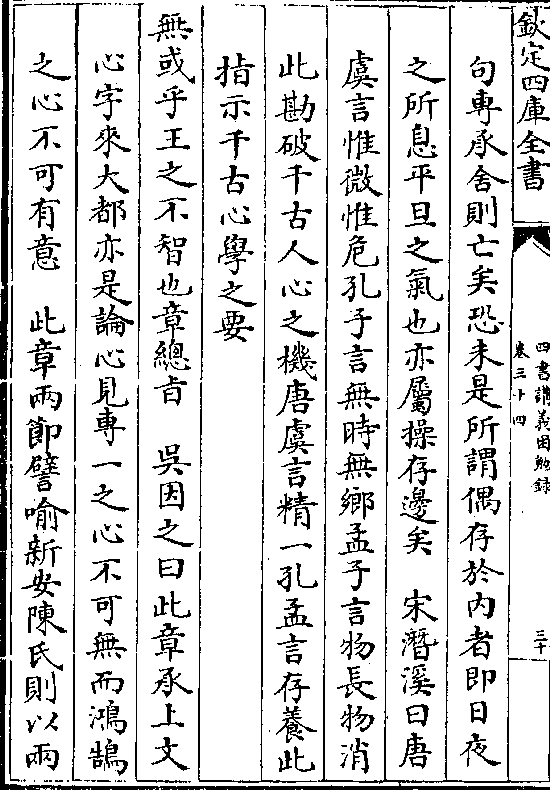 赖多暴律之也
赖多暴律之也今夫麰麦节 四书脉曰人都以地同时同熟同谓足
明降才之同余谓不然须知麰麦美种原含生意其
种之美同故得地得时则其生其熟自同人性皆善
苟无所陷溺其心而培其生机则人人皆可为圣即
麰麦之熟有不同必有不齐处人之远于圣必是陷
溺其心而操存之功与圣异也 翼注曰麰麦节常
卷三十四 第 21a 页 WYG0209-0720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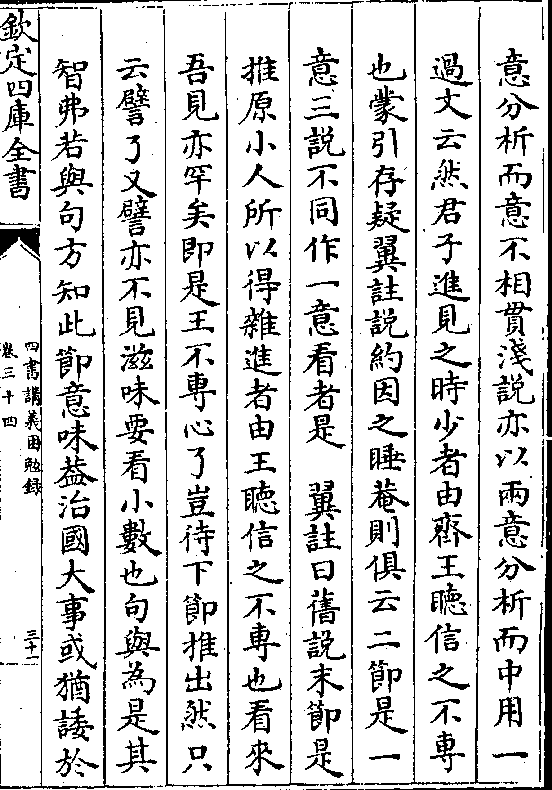 说云其地同性之所宜同也时又同性之所育同也
说云其地同性之所宜同也时又同性之所育同也日至皆熟性之所成同也丘月林云只重皆熟句不
必作三同甚是 按此与四书脉同但此云只重皆
熟句不若脉兼重其生其熟更完也蒙引存疑浅说
大约皆主三同之说不是 附蒙引曰今夫麰麦播
种而耰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浡然而生至于日至
之时皆熟矣何尝有不同虽其间不能无多寡之不
同则以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在麰麦
岂有不同哉总见同类相似之意不必依新安陈氏
卷三十四 第 21b 页 WYG0209-0720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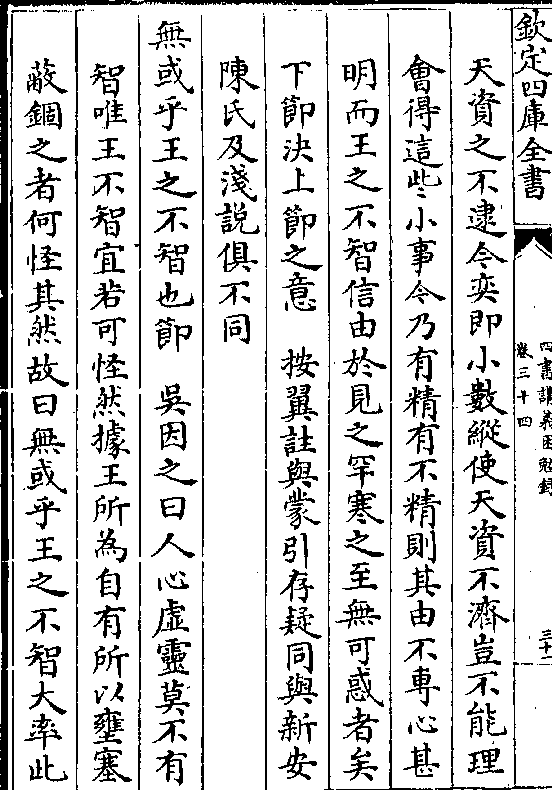 以此譬降才同而养其心与陷溺其心有不同也观
以此譬降才同而养其心与陷溺其心有不同也观下文接云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可见盖所谓养其
心与陷溺其心之不同意皆在言外通一章看可见
盖圣人与我同类而人心皆同然乎理义如此然则
其所以不同者非以陷溺其心乎 按蒙引此条甚
拘只依新安陈氏为是四书脉亦本新安也 湖南
讲曰麰麦播种时地俱同则其生熟亦同 地有肥
卷三十四 第 22a 页 WYG0209-0721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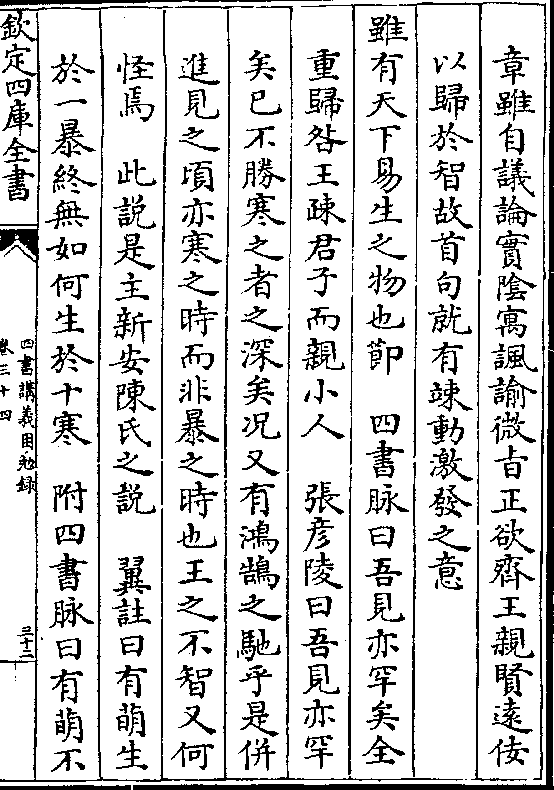 硗三句三平看每句内皆有不齐意然不必以第三
硗三句三平看每句内皆有不齐意然不必以第三句不齐二字总承也大全蒙引存疑浅说翼注说约
等书皆无明训愚看来当如此 张彦陵曰究竟说
不同处正要发明他同处
故凡同类者节 翼注曰同类以形言相似以性言圣
人与我同是人类就形说而含性意 张彦陵曰愚
按吾人不肯合下承当只此疑根作阻孟子曰何独
至于人而疑之喝出本来面目何处更著圣凡二相
卷三十四 第 22b 页 WYG0209-0721b.png
 附四书脉曰圣人与我同类只说同一人类而性
附四书脉曰圣人与我同类只说同一人类而性无不同意尚含蓄未露 按依集注蒙引存疑浅说
即露出亦不妨但只宜轻发耳
故龙子曰节 乐天斋翼注曰故龙子故字承圣人与
我同类来
口之于味四节 四书脉谓子都即郑大夫公孙阏
乐天斋翼注曰故曰六句乃孟子收上文语点醒同
字以起心之同然意先字对陷溺之后言非是圣人
卷三十四 第 23a 页 WYG0209-0721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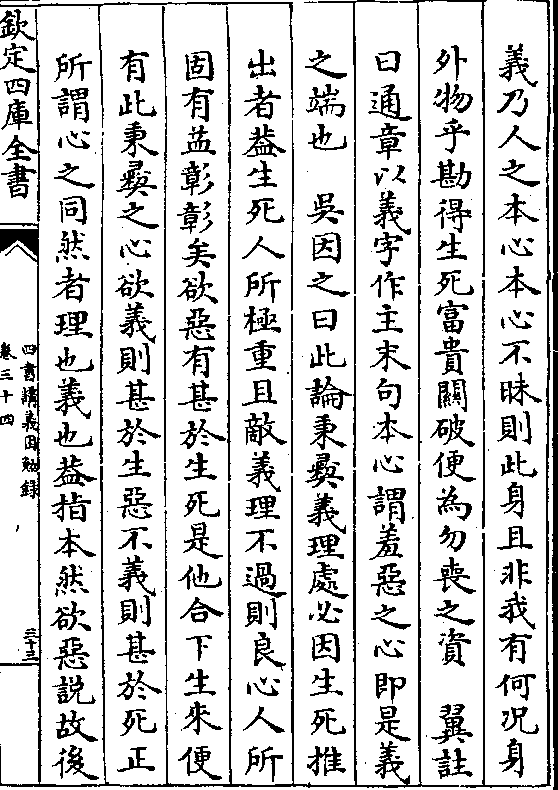 先得此理义而人后得之也降才原无先后也故理
先得此理义而人后得之也降才原无先后也故理义故字紧顶上来非重悦之深只重悦之同上此二
句皆要见得自有而自悦之非悦在外者 四书脉
曰先得句要剔一先字众人陷溺须触此理才见其然
便属后得圣人不为物溺未触以先原无不然即先
得也讲内要点说圣人只先得非独得醒出圣凡同
然意不重圣人先得上故理义故字顶此句说唯人
之心与圣人同故其悦乎理义者亦同 吴因之曰
末节理义二字要说得重见礼义是天地间至纯不
卷三十四 第 23b 页 WYG0209-0721d.png
 杂至粹无疵的人心所同然就是这个物件要在此
杂至粹无疵的人心所同然就是这个物件要在此处隐隐藏得个性善的意思乃佳 徐岩泉曰心遇
理义自然悦不待使心到理义上(此即指恻隐羞恶之类)口遇
刍豢自然悦不待使心到刍豢上天机之妙不待安
排 张彦陵曰按刍豢句昔解只说是例其同时解
乃并说是例其悦之妙要之唯其妙于自然斯见其
为同然若悦处有所勉强有所假借便有然有不然
卷三十四 第 24a 页 WYG0209-0722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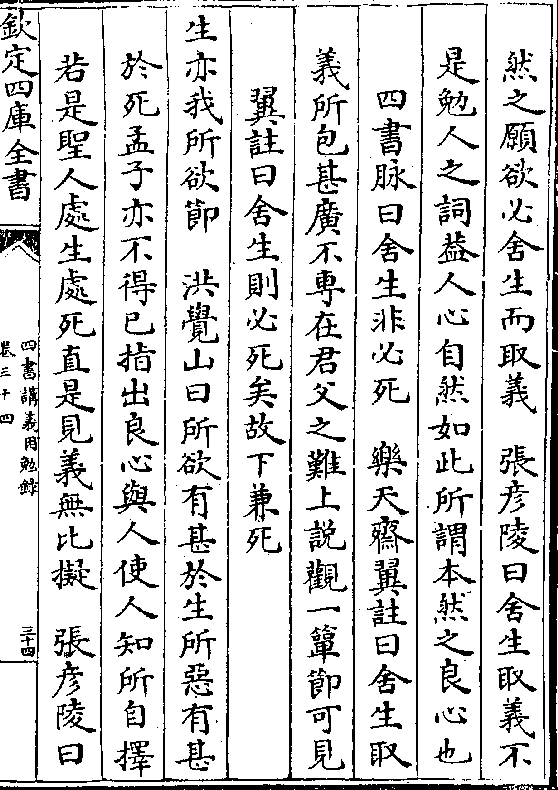 又安所得同 如此看则同然意当在言外补出矣
又安所得同 如此看则同然意当在言外补出矣亦未是愚意此二句当重两我字盖理义悦心在圣
人固如此也而在我心亦如此是即所谓同然也不
必在言外见同然意 吴因之曰章内相似字面及
诸同字俱是大关键处然此章专为性善而发乃不
徒言性善而必深著其同者盖人至圣而极圣且与
我不异是人性之皆善也明矣 又曰此章全重心
言心正所以言性也心性原不是两个故曰尽其心
者知其性 又曰以心明性以心之同然理义明性
卷三十四 第 24b 页 WYG0209-0722b.png
 善此孟子论性最精切处 按以心之同然理义明
善此孟子论性最精切处 按以心之同然理义明性善即与上章以情徵性同
牛山之木尝美矣章总旨 乐天斋翼注曰通章即山
木以著人心失养之害而申言其系于养末引言人
心之难养以见其当养也
牛山之木尝美矣节 梁无知曰以其郊于大国句最
宜著眼正斧斤牛羊所自来也老子曰不见可欲使
卷三十四 第 25a 页 WYG0209-0722c.png
 心不乱亦避大国之意也 圣贤学问又不必专以
心不乱亦避大国之意也 圣贤学问又不必专以避为事 看来未伐而保之已伐而复之两层意亦
俱重何必专重下一层 乐天斋翼注曰润即润其
所息也
虽存乎人者节 张彦陵曰虽存乎人者虽字照下违
禽兽不远看非承上山木来不直曰有仁义而曰岂
无仁义是就放失后追论未失之前如此 依此则
人字就不好人说矣此本吴因之与蒙引又不同与
存疑亦不同 附蒙引曰虽存乎人者二句承上文
卷三十四 第 25b 页 WYG0209-0722d.png
 言山之必有材此在山者然也虽然在人者亦岂无
言山之必有材此在山者然也虽然在人者亦岂无仁义之心哉 附翼注曰其日夜之所息与上节不
同此只重夜字 按浅说亦与翼注同俱不是日夜
二字只平说盖此句内不必遽重在夜也 刘上玉
曰其日夜句大全诸子及诸讲俱说夜气清足以生
息尚未妥气字在下句此句不当说本注自明 按
其日夜句亦有气在内但不专主于气耳 翼注曰
卷三十四 第 26a 页 WYG0209-0723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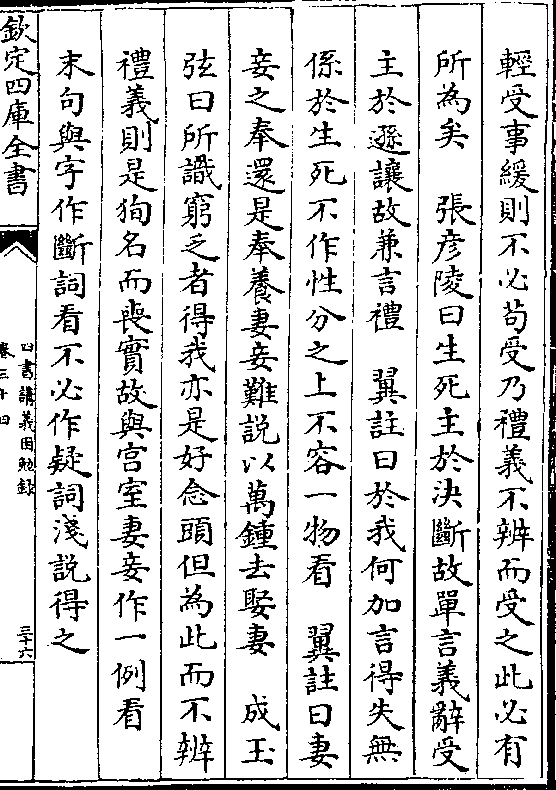 好恶与人相近好在仁义恶在不仁不义也 又曰
好恶与人相近好在仁义恶在不仁不义也 又曰仁义是性好恶是情能好恶是才 徐自溟曰与人
相近是自觉非人见 郑豁渠曰人所谓本来人也
四书脉曰夜气即是才 李衷一曰圣人无夜气
以其常清常明也众人良心放失日间好恶必是拂
人之性直至夜来睡寐之时前念已往后念未兴积
至平旦睡寐初醒尚有一点灵明透露出来直是人
元来的心忽自障翳自现出 李见罗曰孟子论良
心多于卒然有感之际验之如入井之见而恻隐生
卷三十四 第 26b 页 WYG0209-0723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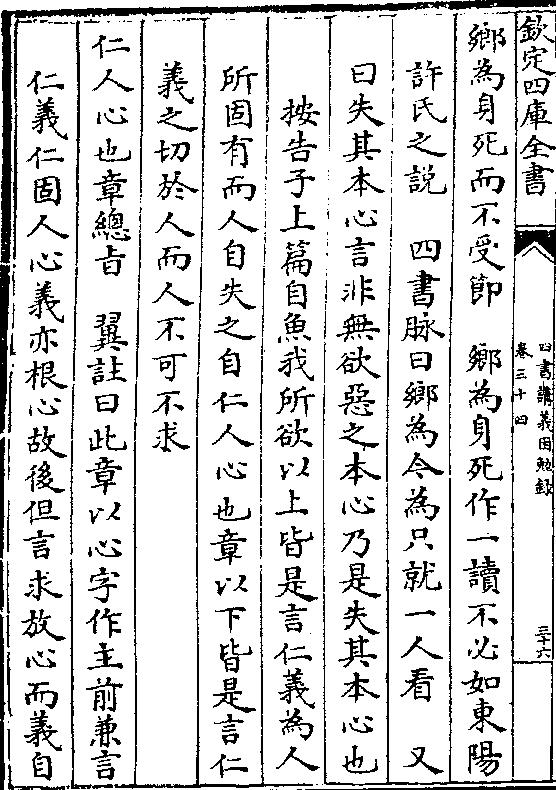 嘑蹴之与而羞恶生皆天机之自然骤感骤应不容
嘑蹴之与而羞恶生皆天机之自然骤感骤应不容强为者也然必乍见嘑蹴而后有是心则非乍见嘑
蹴之时泯矣故特提夜气二字以验人心之真 湖
南讲曰从来论学问者率多指心今论到气似反说
粗了不知心惟有养的方心能作主心不曾有养的
反听凭著气盖心乘乎气气清则心与之俱清气昏
则心与之俱昏 浩然之气是通一身之气夜气是
卷三十四 第 27a 页 WYG0209-0723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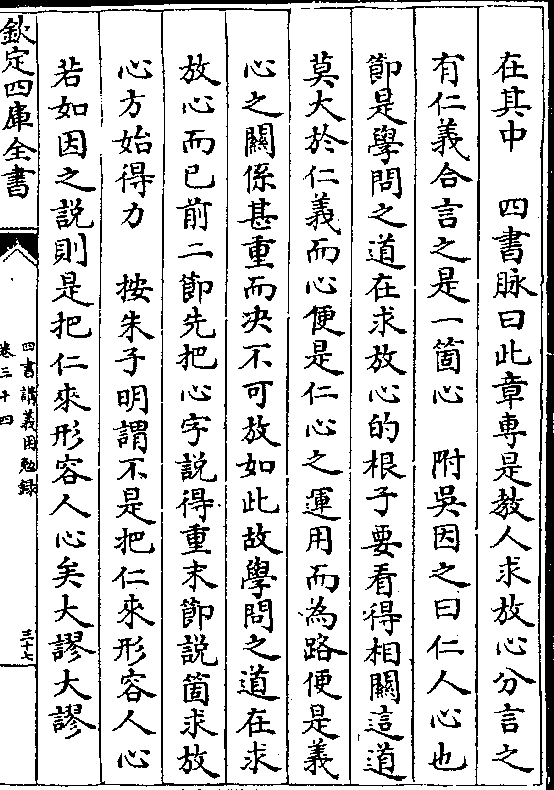 此心精英之气大全云峰胡氏东阳许氏俱牵浩气
此心精英之气大全云峰胡氏东阳许氏俱牵浩气来说恐未是 右愚初见如此然看来夜气亦似通
一身之气言即依云峰东阳说自妙也 张彦陵曰
初学须在平常心中认识出本心来做主脑此最是
初入门一段要紧路径本心虽汨没其实有不容泯
灭处常因时发见学者但要识取耳平旦好恶孩提
爱敬乍见恻隐生死欲恶皆孟子教人识本心处若
不当面错过时时应有入路 孟子言性之善则验
之情言情之善则验之乍见之孺子平旦之好恶孩
卷三十四 第 27b 页 WYG0209-0723d.png
 提之知能妙妙 梏之反覆不可谓夜之所息而旦
提之知能妙妙 梏之反覆不可谓夜之所息而旦昼梏之旦昼所息夜又梏之也须如浅说云昨夜所
息而今日梏之今夜所息而明日梏之蒙引存疑亦
甚明 朱子曰夜气不足以存不足以存此心耳非
谓存夜气也若存得这个心则气自清 吴因之日夜
气不足以存正与日夜之所息一句相反存字要说
得细盖当良心放失之后犹有日夜所息是良心既
卷三十四 第 28a 页 WYG0209-0724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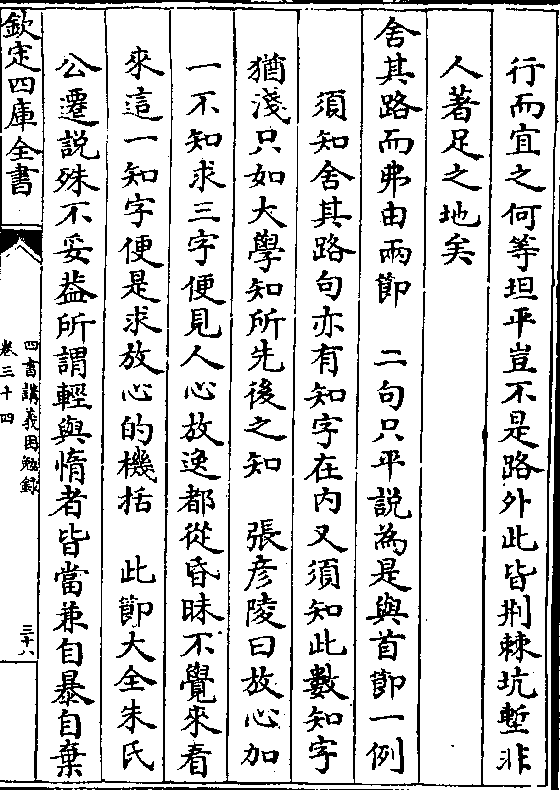 绝而复续既往而复来有既亡而复存意故云存至
绝而复续既往而复来有既亡而复存意故云存至于梏之反覆则并夜间亦无所生息直是绝不复续
往不复来亡不复存矣故曰不足以存就其无所生
息处便是不足以存非两层 按因之说甚明但谓
夜气不足以存与日夜之所息一句相反稍欠完备
一字当改作三字 张彦陵曰违禽兽不远对与人
相近看盖禽兽有知无良人无良心其所存者亦只
是知觉运动故与禽兽不远 观此乃知孟子动辄
以禽兽比人不是骂人乃实理如此
卷三十四 第 28b 页 WYG0209-0724b.png
 故苟得其养节 翼注曰养字兼未失而保之既失而
故苟得其养节 翼注曰养字兼未失而保之既失而复之物字所包者广山木人心在内只虚虚浑说为
妙 四书脉曰长不在维持之久消不待渐摩之久
只一念自为转移耳
操则存节 翼注曰上四句悬空说末句方可露心字
四书镜曰道心人心相为消长 蒙训曰孔子当
日只是状人之心是个极员活的物事尚未言及操
卷三十四 第 29a 页 WYG0209-0724c.png
 心不舍之法 四书脉曰末节不重形容心之神重
心不舍之法 四书脉曰末节不重形容心之神重在欲人存养意 张彦陵曰操舍只以理欲言此心
在天理上便是存此心在人欲上便是亡存亡便是
出入盖天理是心之窟宅所谓神明之舍也出入云
者出入于神明之舍耳 王阳明曰若论本体原是
无出无入的 此即范淳夫女心岂有出入之说程
子虽取之然未尝以为孟子本文正解也阳明则便
以为孟子正解矣谬甚盖此节不是论心之本体也
观大全朱子说自明 王阳明云出入无时二句学
卷三十四 第 29b 页 WYG0209-0724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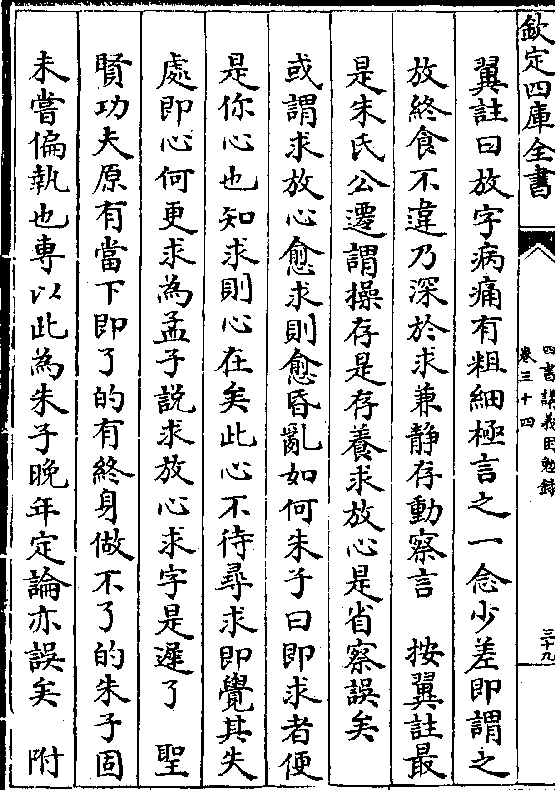 者要知得心之本体原是如此不可便谓出为亡入
者要知得心之本体原是如此不可便谓出为亡入为存云云此说从程子心本无出入句生来说非不
精但常人之心岂能日应万事而原无出入须是操
存得手的方有此境界耳亦与孟子引来警戒凡人
意不合故断以朱说为长又考大全中有一条云问
范淳夫女云云观此条则朱子非不知此说但此处
论心不当如是精言故不用耳 又曰居业录云孟
卷三十四 第 30a 页 WYG0209-0725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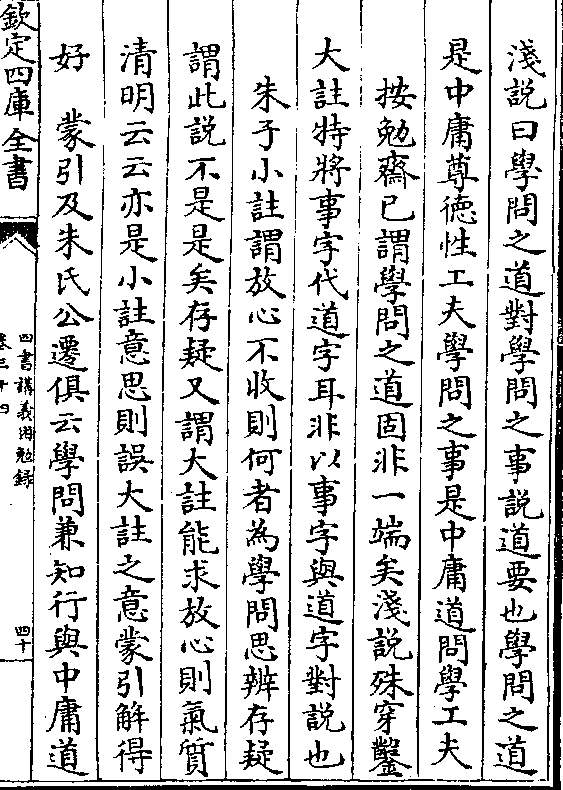 子求放心操则存者只是约束收敛不放纵使内有
子求放心操则存者只是约束收敛不放纵使内有主而已与禅家常看管一个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
此者相似而实不同收敛有主则心体昭然遇事时
鉴察必精若守著一个光明的心则人伦世事都不
管 湖南讲曰前边说气谓何又说操心可见养气
时仍在那里提摄此心人能操存得心则气自随他
转 大全朱子谓不能操而存之则其出而逐物于
外与其偶存于内者皆荒忽无常似将出入无时二
句专承舍则亡矣恐未是所谓偶存于内者即日夜
卷三十四 第 30b 页 WYG0209-0725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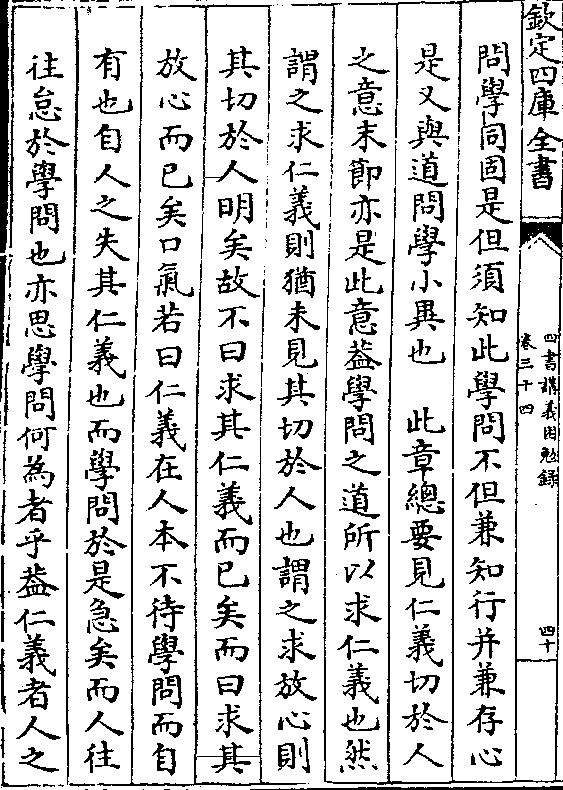 之所息平旦之气也亦属操存边矣 宋潜溪曰唐
之所息平旦之气也亦属操存边矣 宋潜溪曰唐虞言惟微惟危孔子言无时无乡孟子言物长物消
此勘破千古人心之机唐虞言精一孔孟言存养此
指示千古心学之要
无或乎王之不智也章总旨 吴因之曰此章承上文
心字来大都亦是论心见专一之心不可无而鸿鹄
之心不可有意 此章两节譬喻新安陈氏则以两
卷三十四 第 31a 页 WYG0209-0725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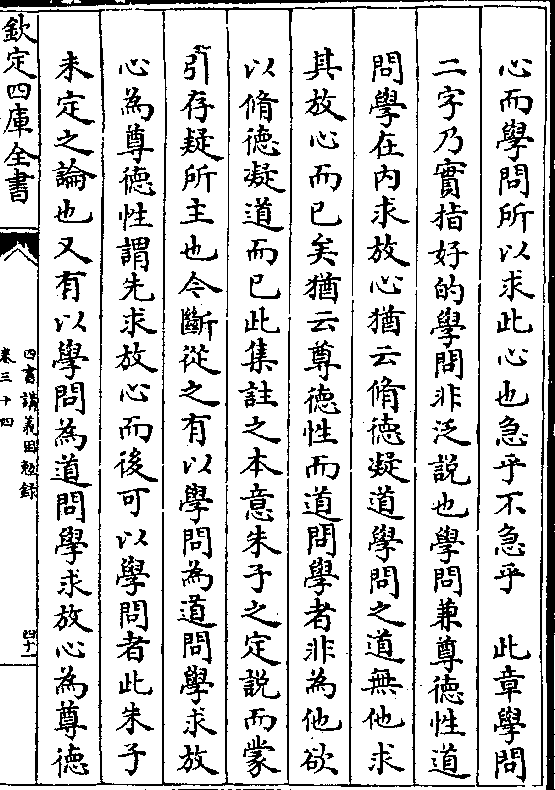 意分析而意不相贯浅说亦以两意分析而中用一
意分析而意不相贯浅说亦以两意分析而中用一过文云然君子进见之时少者由齐王听信之不专
也蒙引存疑翼注说约因之睡庵则俱云二节是一
意三说不同作一意看者是 翼注曰旧说末节是
推原小人所以得杂进者由王听信之不专也看来
吾见亦罕矣即是王不专心了岂待下节推出然只
云譬了又譬亦不见滋味要看小数也句与为是其
智弗若与句方知此节意味盖治国大事或犹诿于
天资之不逮今奕即小数纵使天资不济岂不能理
卷三十四 第 31b 页 WYG0209-0725d.png
 会得这些小事今乃有精有不精则其由不专心甚
会得这些小事今乃有精有不精则其由不专心甚明而王之不智信由于见之罕寒之至无可惑者矣
下节决上节之意 按翼注与蒙引存疑同与新安
陈氏及浅说俱不同
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节 吴因之曰人心虚灵莫不有
智唯王不智宜若可怪然据王所为自有所以壅塞
蔽锢之者何怪其然故曰无或乎王之不智大率此
卷三十四 第 32a 页 WYG0209-0726a.png
 章虽自议论实阴寓讽谕微旨正欲齐王亲贤远佞
章虽自议论实阴寓讽谕微旨正欲齐王亲贤远佞以归于智故首句就有竦动激发之意
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节 四书脉曰吾见亦罕矣全
重归咎王疏君子而亲小人 张彦陵曰吾见亦罕
矣已不胜寒之者之深矣况又有鸿鹄之驰乎是并
进见之顷亦寒之时而非暴之时也王之不智又何
怪焉 此说是主新安陈氏之说 翼注曰有萌生
于一暴终无如何生于十寒 附四书脉曰有萌不
必说孟子见王时乃有萌此说齐王本心灵根不死
卷三十四 第 32b 页 WYG0209-0726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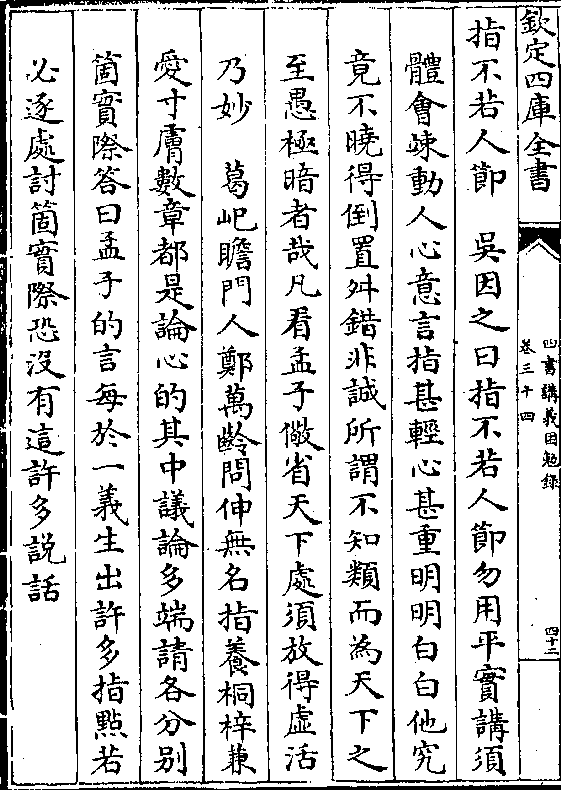 有触即生即放失之后而萌蘖自生
有触即生即放失之后而萌蘖自生今夫奕之为数节 张彦陵曰即王心亦有萌处便见
非智之不若人 四书脉曰末节重学奕不重诲奕
上 又曰专心者心专于奕而不他也致志者求至
奕秋而后已
鱼我所欲也章总旨 四书脉曰此章以本心二字为
主上六节言人有本心末二节伤人失本心舍生取
卷三十四 第 33a 页 WYG0209-0726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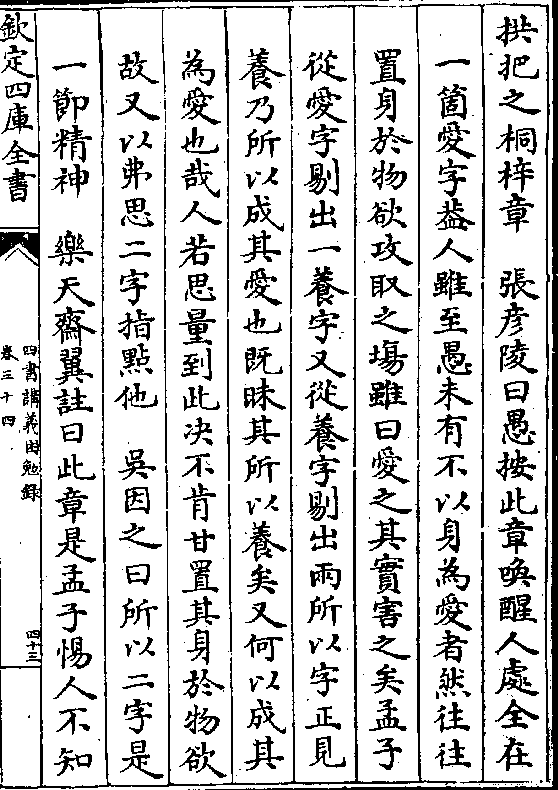 义乃人之本心本心不昧则此身且非我有何况身
义乃人之本心本心不昧则此身且非我有何况身外物乎勘得生死富贵关破便为勿丧之资 翼注
曰通章以义字作主末句本心谓羞恶之心即是义
之端也 吴因之曰此论秉彝义理处必因生死推
出者盖生死人所极重且敌义理不过则良心人所
固有益彰彰矣欲恶有甚于生死是他合下生来便
有此秉彝之心欲义则甚于生恶不义则甚于死正
所谓心之同然者理也义也盖指本然欲恶说故后
曰本心
卷三十四 第 33b 页 WYG0209-0726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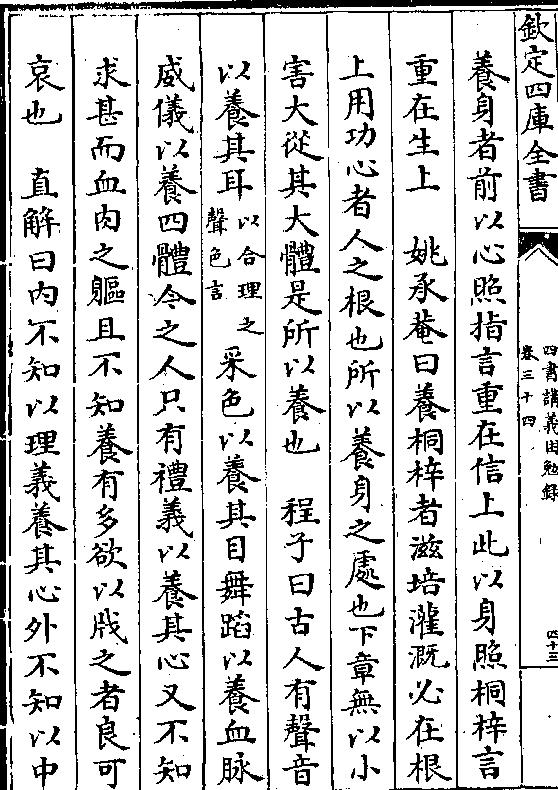 鱼我所欲也节 四书镜曰首节四个所欲且勿露熊
鱼我所欲也节 四书镜曰首节四个所欲且勿露熊掌尤美义尤重意此意还在下文 所谓二者不可
得兼固不止谓簟食豆羹得生失死之际然箪食豆
羹得生失死之际亦在其内新安陈氏以为是说托
孤寄命之大节时事拘矣 乐天斋翼注曰生与义
为何不得兼就遇变难处言欲全生则害义欲全义
则捐生如何兼得既不可兼则有舍取吾度人心自
卷三十四 第 34a 页 WYG0209-0727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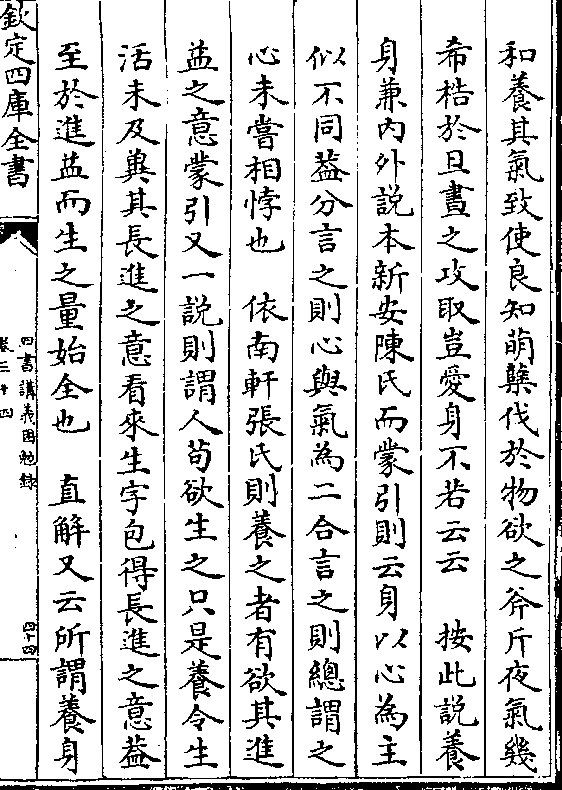 然之愿欲必舍生而取义 张彦陵曰舍生取义不
然之愿欲必舍生而取义 张彦陵曰舍生取义不是勉人之词盖人心自然如此所谓本然之良心也
四书脉曰舍生非必死 乐天斋翼注曰舍生取
义所包甚广不专在君父之难上说观一箪节可见
翼注曰舍生则必死矣故下兼死
生亦我所欲节 洪觉山曰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
于死孟子亦不得已指出良心与人使人知所自择
若是圣人处生处死直是见义无比拟 张彦陵曰
两甚字虽指义不义说本文却不道破 即明点义
卷三十四 第 34b 页 WYG0209-0727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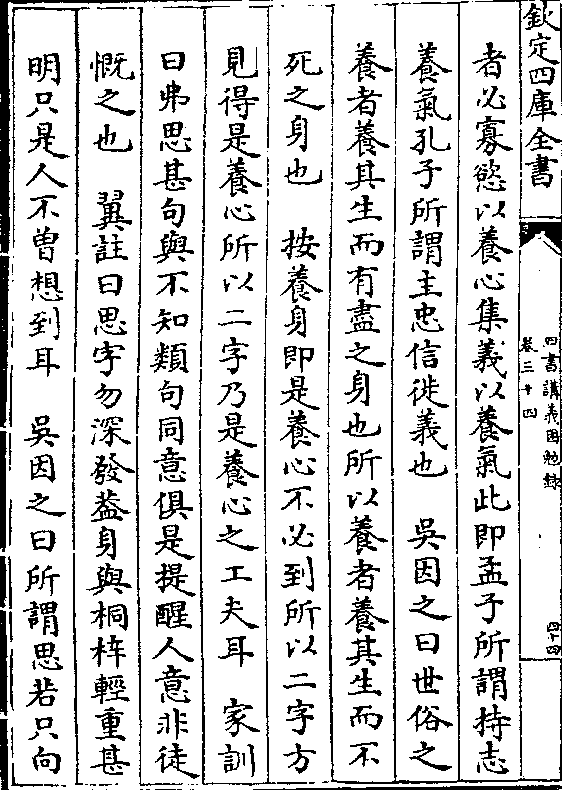 字亦何妨浅说亦明点义字 乐天斋翼注曰首二
字亦何妨浅说亦明点义字 乐天斋翼注曰首二节重一义字注云秉彝之良心是也良心即末节本
心也
如使人之所欲两节 如使节是反言以见良心之必
有不是反言以见良心之不可无玩庆源辅氏说亦
可见 翼注曰第三四节不过即次节之义而反覆
言之
卷三十四 第 35a 页 WYG0209-0727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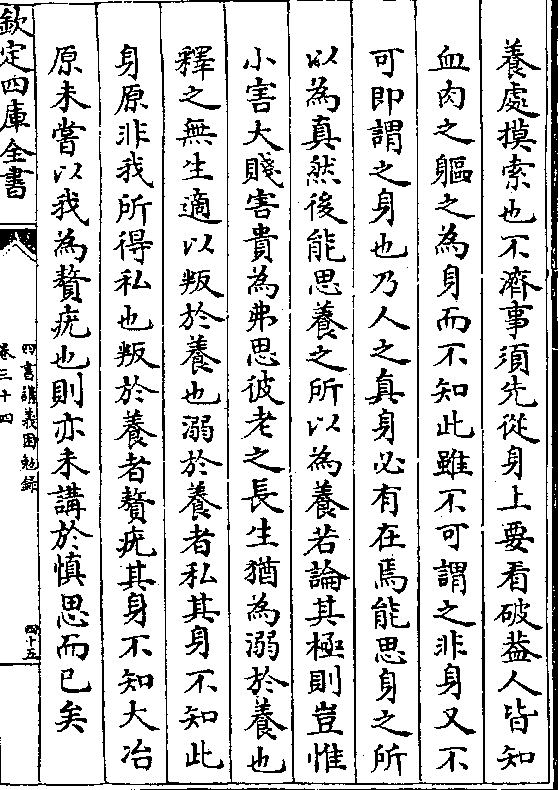 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节 张彦陵曰是故二字结上
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节 张彦陵曰是故二字结上起下重人皆有之句然贤者能勿丧耳亦非带言惟
贤者但能勿丧见彼不能勿丧者非本无也
一箪食节 徐儆弦曰人之舍生取义必有一个真心
激发处方能抛得身子所以拈出嘑蹴二字作话头
然贤者之激发其心处与众人不同若众人则不至
嘑尔蹴尔其真心亦不能即发见也 沈无回曰不
受嘑蹴之心如电光忽过景不及搏稍落第二念则
心扰万虑而未必不受矣此不受的人与下受无礼
卷三十四 第 35b 页 WYG0209-0727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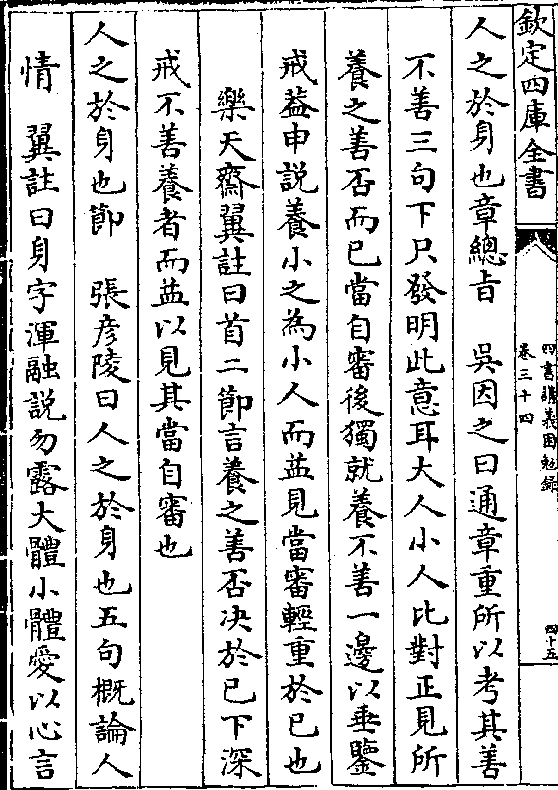 义之万钟的人作一等人看 孟子亦就陷溺的人
义之万钟的人作一等人看 孟子亦就陷溺的人说若贤者则时时是礼义岂待嘑蹴之时方见得
乐天斋翼注曰不受不屑之心不可指定行人乞
人说只是虽行乞且激于义而不苟受况非行乞者
乎
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节 卢未人曰万钟对箪豆
看轻重不同何加对生死看缓急不同物重则不当
卷三十四 第 36a 页 WYG0209-0728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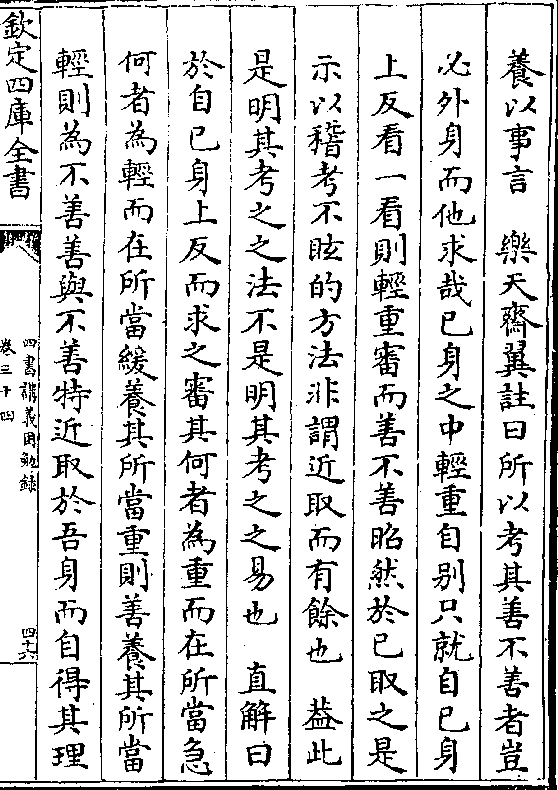 轻受事缓则不必苟受乃礼义不辨而受之此必有
轻受事缓则不必苟受乃礼义不辨而受之此必有所为矣 张彦陵曰生死主于决断故单言义辞受
主于逊让故兼言礼 翼注曰于我何加言得失无
系于生死不作性分之上不容一物看 翼注曰妻
妾之奉还是奉养妻妾难说以万钟去娶妻 成玉
弦曰所识穷乏者得我亦是好念头但为此而不辨
礼义则是徇名而丧实故与宫室妻妾作一例看
末句与字作断词看不必作疑词浅说得之
乡为身死而不受节 乡为身死作一读不必如东阳
卷三十四 第 36b 页 WYG0209-0728b.png
 许氏之说 四书脉曰乡为今为只就一人看 又
许氏之说 四书脉曰乡为今为只就一人看 又曰失其本心言非无欲恶之本心乃是失其本心也
按告子上篇自鱼我所欲以上皆是言仁义为人
所固有而人自失之自仁人心也章以下皆是言仁
义之切于人而人不可不求
仁人心也章总旨 翼注曰此章以心字作主前兼言
仁义仁固人心义亦根心故后但言求放心而义自
卷三十四 第 37a 页 WYG0209-0728c.png
 在其中 四书脉曰此章专是教人求放心分言之
在其中 四书脉曰此章专是教人求放心分言之有仁义合言之是一个心 附吴因之曰仁人心也
节是学问之道在求放心的根子要看得相关这道
莫大于仁义而心便是仁心之运用而为路便是义
心之关系甚重而决不可放如此故学问之道在求
放心而已前二节先把心字说得重末节说个求放
心方始得力 按朱子明谓不是把仁来形容人心
若如因之说则是把仁来形容人心矣大谬大谬
仁人心也节 翼注曰首节两人字最见仁义切于人
卷三十四 第 37b 页 WYG0209-0728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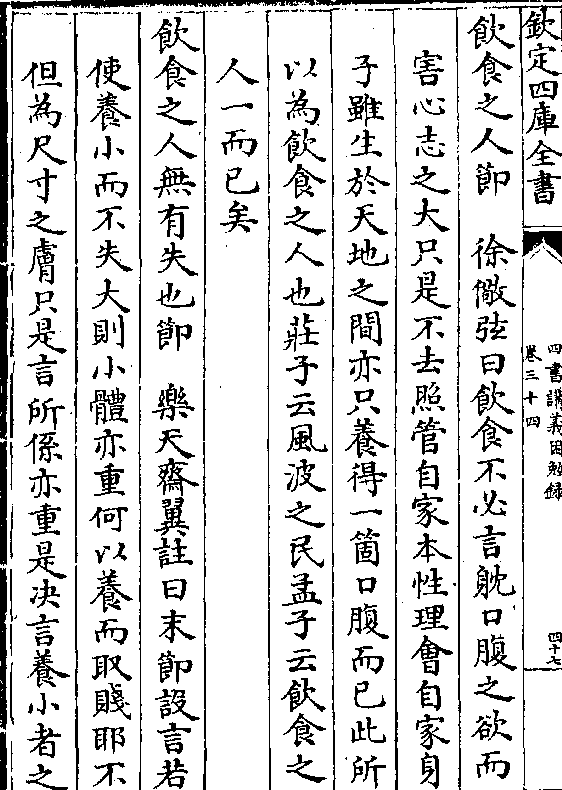 身意葛屺瞻曰仁为善之长并礼义知信俱可该得
身意葛屺瞻曰仁为善之长并礼义知信俱可该得又抽出义来云人路如夫子云复礼为仁便将礼为
仁用孟子平日论事俱以仁义并言便将义为仁用
如阳明致良知又重在知可见个个字俱可提得
注仁则其生之性此以心之德言大全朱子谓生之
性便是爱之理者盖谓爱之理亦是生之性耳非正
解本文也 乐天斋翼注曰义人路将此恻隐之心
卷三十四 第 38a 页 WYG0209-0729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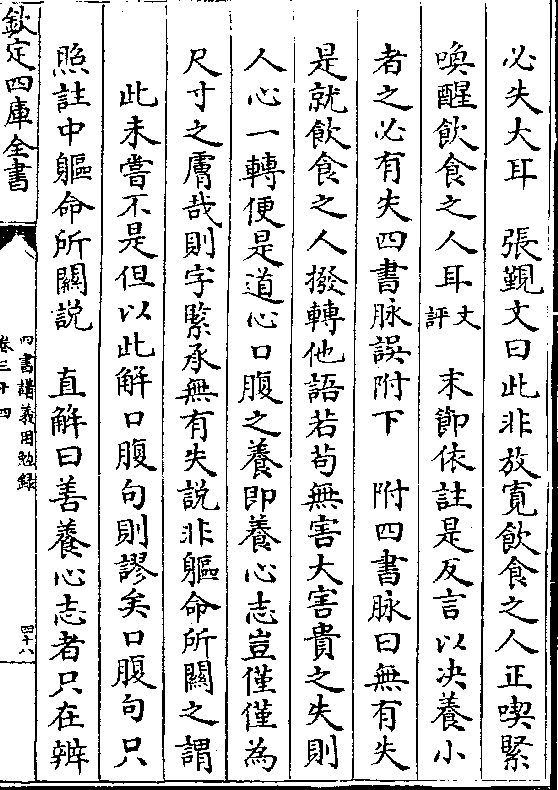 行而宜之何等坦平岂不是路外此皆荆棘坑堑非
行而宜之何等坦平岂不是路外此皆荆棘坑堑非人著足之地矣
舍其路而弗由两节 二句只平说为是与首节一例
须知舍其路句亦有知字在内又须知此数知字
犹浅只如大学知所先后之知 张彦陵曰放心加
一不知求三字便见人心放逸都从昏昧不觉来看
来这一知字便是求放心的机括 此节大全朱氏
公迁说殊不妥盖所谓轻与惰者皆当兼自暴自弃
皆是不肯居仁由义皆是不能求放心公迁分配得
卷三十四 第 38b 页 WYG0209-0729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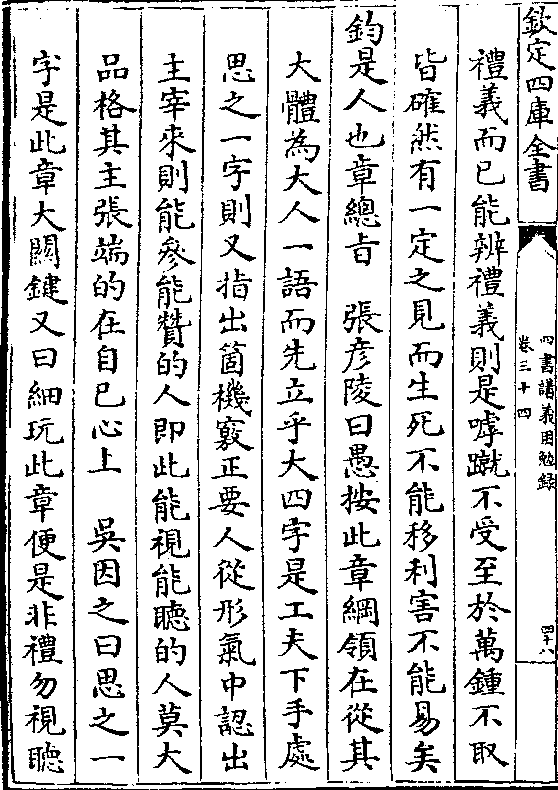 不是
不是学问之道无他节 翼注曰此放字是无形之放盖天
理是心之本体离了本体便是放犹俗云走作了也
放不是放在身外求亦不是向外寻求迷则千里觉
则见在 方孟旋曰放非专驰鹜之谓求非专操存
之谓若不识本来面目求即是放若识得时宁独操
存是收即放下亦是收 汤霍林曰求放心之功有
卷三十四 第 39a 页 WYG0209-0729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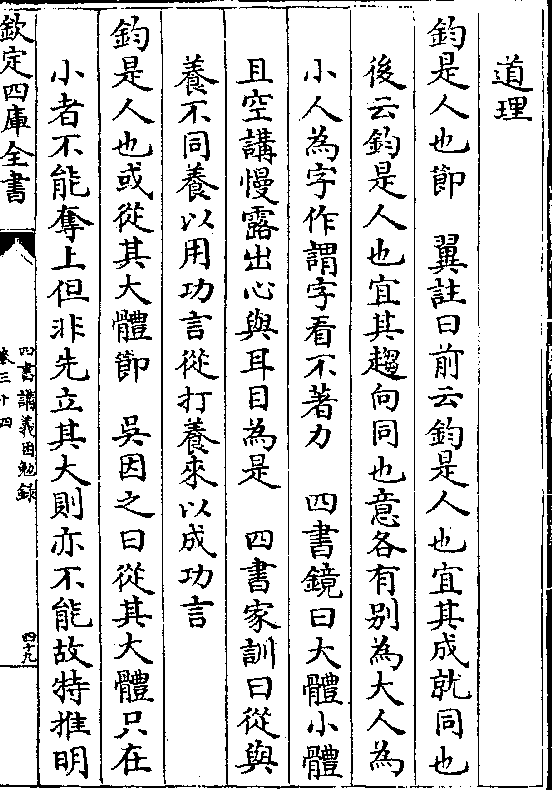 三未放而守之此存养之学问将放而防之此慎独
三未放而守之此存养之学问将放而防之此慎独之学问既放而挽之此善反之学问如此方说得工
夫全 大慧师曰要须内不放出外不放入内不放
出则是内心无喘外不放入即是外息诸缘 鹤林
玉露曰孟子言求放心而康节邵子曰心要能放二
者天渊悬绝盖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大全)
(朱子亦有此意)众人之心易放圣贤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荡
能放者开辟流荡者失其本心开辟者全其本心
翼注曰放字病痛有粗细极言之一念少差即谓之
卷三十四 第 39b 页 WYG0209-0729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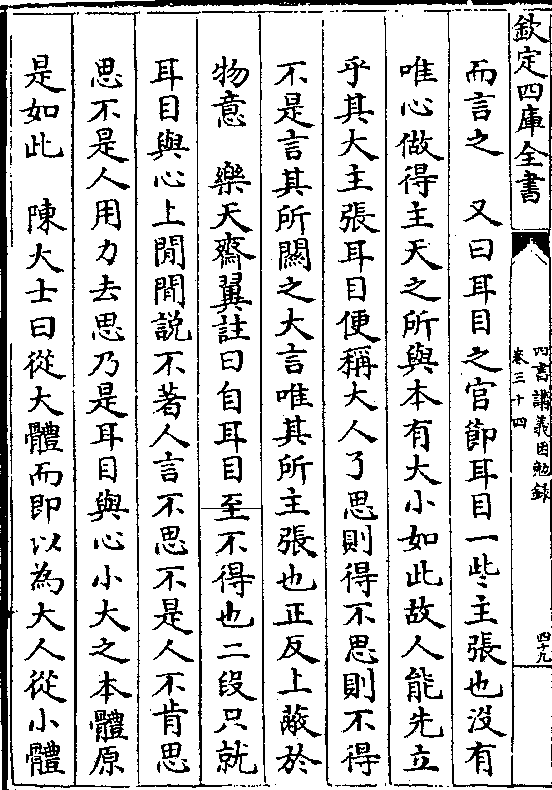 放终食不违乃深于求兼静存动察言 按翼注最
放终食不违乃深于求兼静存动察言 按翼注最是朱氏公迁谓操存是存养求放心是省察误矣
或谓求放心愈求则愈昏乱如何朱子曰即求者便
是你心也知求则心在矣此心不待寻求即觉其失
处即心何更求为孟子说求放心求字是迟了 圣
贤功夫原有当下即了的有终身做不了的朱子固
未尝偏执也专以此为朱子晚年定论亦误矣 附
卷三十四 第 40a 页 WYG0209-0730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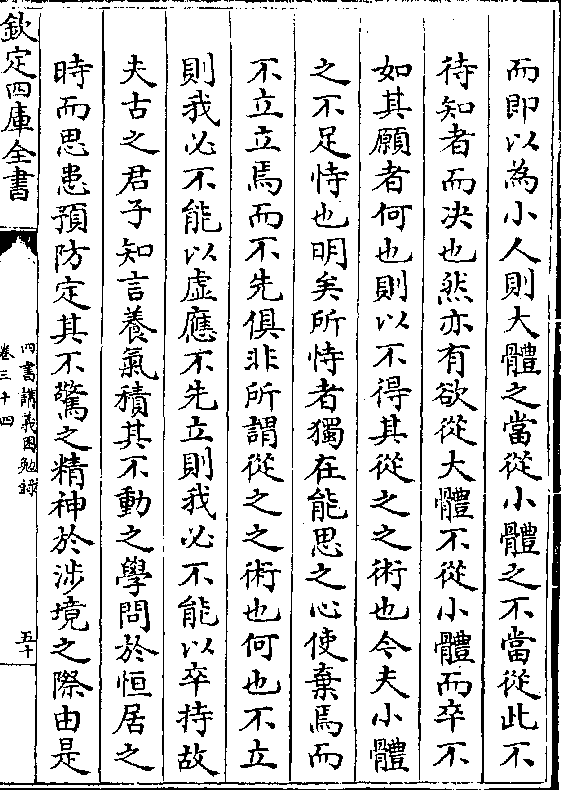 浅说曰学问之道对学问之事说道要也学问之道
浅说曰学问之道对学问之事说道要也学问之道是中庸尊德性工夫学问之事是中庸道问学工夫
按勉斋已谓学问之道固非一端矣浅说殊穿凿
大注特将事字代道字耳非以事字与道字对说也
朱子小注谓放心不收则何者为学问思辨存疑
谓此说不是是矣存疑又谓大注能求放心则气质
清明云云亦是小注意思则误大注之意蒙引解得
好 蒙引及朱氏公迁俱云学问兼知行与中庸道
问学同固是但须知此学问不但兼知行并兼存心
卷三十四 第 40b 页 WYG0209-0730b.png
 是又与道问学小异也 此章总要见仁义切于人
是又与道问学小异也 此章总要见仁义切于人之意末节亦是此意盖学问之道所以求仁义也然
谓之求仁义则犹未见其切于人也谓之求放心则
其切于人明矣故不曰求其仁义而已矣而曰求其
放心而已矣口气若曰仁义在人本不待学问而自
有也自人之失其仁义也而学问于是急矣而人往
往怠于学问也亦思学问何为者乎盖仁义者人之
卷三十四 第 41a 页 WYG0209-0730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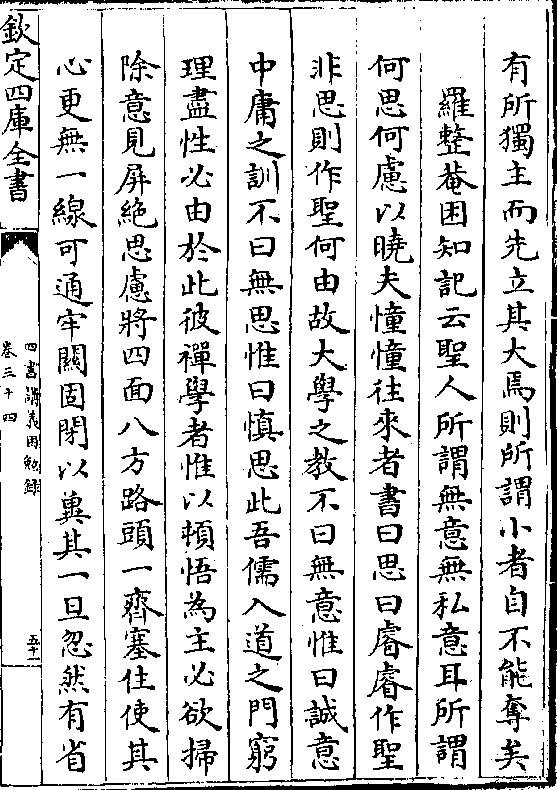 心而学问所以求此心也急乎不急乎 此章学问
心而学问所以求此心也急乎不急乎 此章学问二字乃实指好的学问非泛说也学问兼尊德性道
问学在内求放心犹云脩德凝道学问之道无他求
其放心而已矣犹云尊德性而道问学者非为他欲
以脩德凝道而已此集注之本意朱子之定说而蒙
引存疑所主也今断从之有以学问为道问学求放
心为尊德性谓先求放心而后可以学问者此朱子
未定之论也又有以学问为道问学求放心为尊德
性而谓学问亦所以求放心者此亦依傍朱子未定
卷三十四 第 41b 页 WYG0209-0730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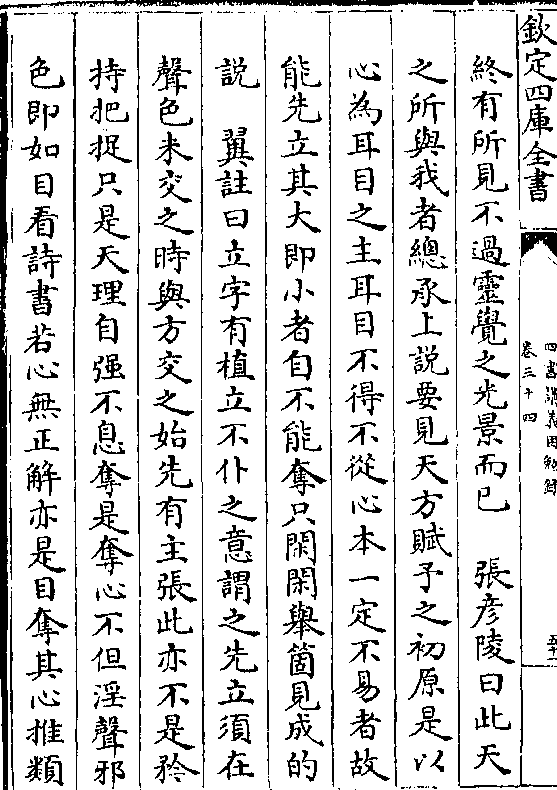 之论而为之者也又有以学问二字虚说谓求放心
之论而为之者也又有以学问二字虚说谓求放心便是学问而以尊德性为求放心抹去道问学一边
者此象山阳明之说也若浅说则又以学问之道对
学问之事说此误看集注之意也若吴因之则又云
义与仁并重均之不可失却究竟只一求放心便都
完事了故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尤
为穿凿也凡此五说俱不可从 凡圣贤说存心有
卷三十四 第 42a 页 WYG0209-0731a.png
 与穷理养性对说者有包穷理养性说者此章与前
与穷理养性对说者有包穷理养性说者此章与前后诸章说存心俱是包穷理养性说
今有无名之指节 姚承庵曰人心本信于万物之上
今却屈于物欲而不能信故借指之屈信为喻 陈
伯玉曰屈而不伸处不可说指之通害若通害又何
以云不若人哉 直解曰于身非有疾痛之苦于事
未为举动之害 张彦陵曰心之若人只提醒方寸
之间便是故以不远秦楚之路影说
指不若人节 吴因之曰指不若人节勿用平实讲须
卷三十四 第 42b 页 WYG0209-0731b.png
 体会竦动人心意言指甚轻心甚重明明白白他究
体会竦动人心意言指甚轻心甚重明明白白他究竟不晓得倒置舛错非诚所谓不知类而为天下之
至愚极暗者哉凡看孟子儆省天下处须放得虚活
乃妙 葛屺瞻门人郑万龄问伸无名指养桐梓兼
爱寸肤数章都是论心的其中议论多端请各分别
个实际答曰孟子的言每于一义生出许多指点若
必逐处讨个实际恐没有这许多说话
卷三十四 第 43a 页 WYG0209-0731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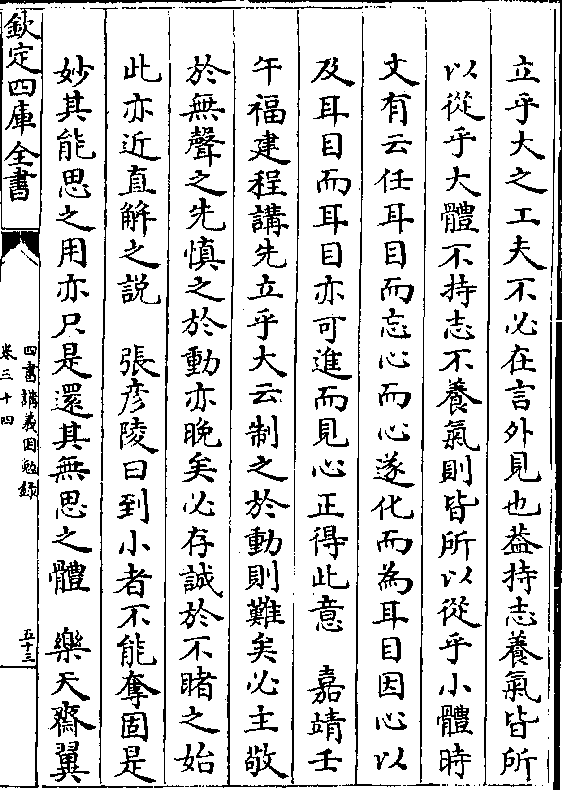 拱把之桐梓章 张彦陵曰愚按此章唤醒人处全在
拱把之桐梓章 张彦陵曰愚按此章唤醒人处全在一个爱字盖人虽至愚未有不以身为爱者然往往
置身于物欲攻取之场虽曰爱之其实害之矣孟子
从爱字剔出一养字又从养字剔出两所以字正见
养乃所以成其爱也既昧其所以养矣又何以成其
为爱也哉人若思量到此决不肯甘置其身于物欲
故又以弗思二字指点他 吴因之曰所以二字是
一节精神 乐天斋翼注曰此章是孟子惕人不知
养身者前以心照指言重在信上此以身照桐梓言
卷三十四 第 43b 页 WYG0209-0731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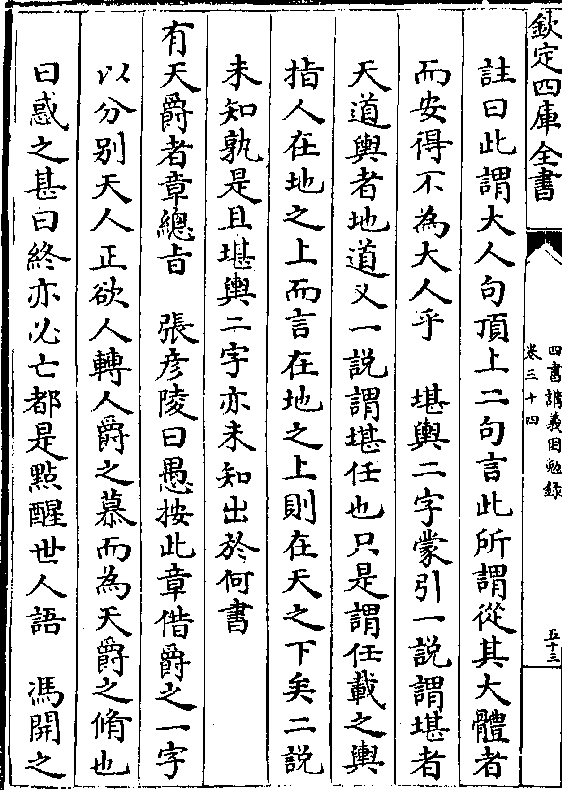 重在生上 姚承庵曰养桐梓者滋培灌溉必在根
重在生上 姚承庵曰养桐梓者滋培灌溉必在根上用功心者人之根也所以养身之处也下章无以小
害大从其大体是所以养也 程子曰古人有声音
以养其耳(以合理之声色言)采色以养其目舞蹈以养血脉
威仪以养四体今之人只有礼义以养其心又不知
求甚而血肉之躯且不知养有多欲以戕之者良可
哀也 直解曰内不知以理义养其心外不知以中
卷三十四 第 44a 页 WYG0209-0732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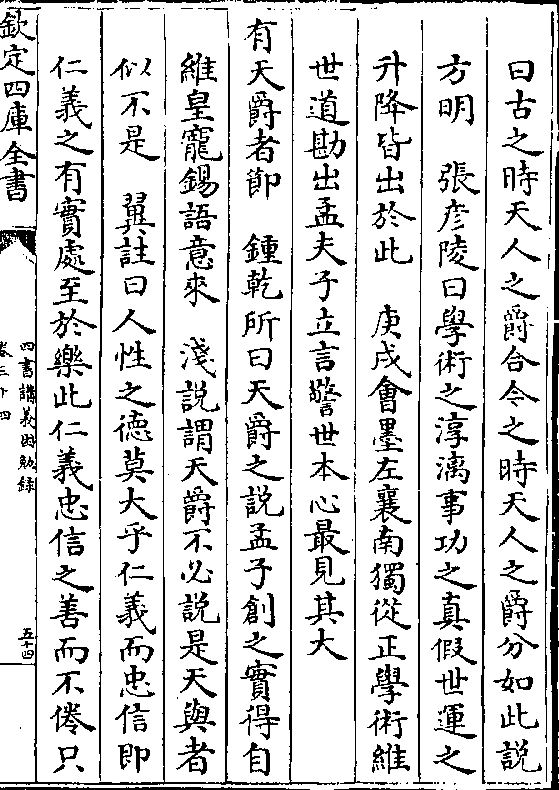 和养其气致使良知萌蘖伐于物欲之斧斤夜气几
和养其气致使良知萌蘖伐于物欲之斧斤夜气几希梏于旦昼之攻取岂爱身不若云云 按此说养
身兼内外说本新安陈氏而蒙引则云身以心为主
似不同盖分言之则心与气为二合言之则总谓之
心未尝相悖也 依南轩张氏则养之者有欲其进
益之意蒙引又一说则谓人苟欲生之只是养令生
活未及冀其长进之意看来生字包得长进之意盖
至于进益而生之量始全也 直解又云所谓养身
者必寡欲以养心集义以养气此即孟子所谓持志
卷三十四 第 44b 页 WYG0209-0732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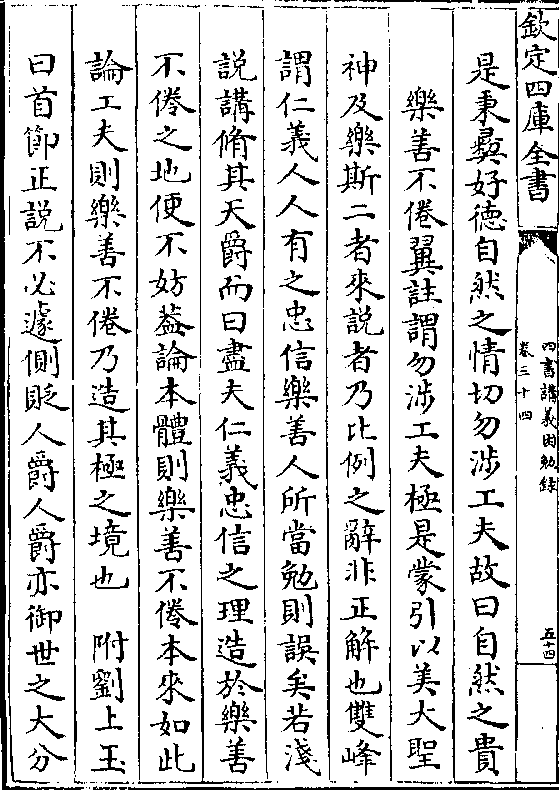 养气孔子所谓主忠信徙义也 吴因之曰世俗之
养气孔子所谓主忠信徙义也 吴因之曰世俗之养者养其生而有尽之身也所以养者养其生而不
死之身也 按养身即是养心不必到所以二字方
见得是养心所以二字乃是养心之工夫耳 家训
曰弗思甚句与不知类句同意俱是提醒人意非徒
慨之也 翼注曰思字勿深发盖身与桐梓轻重甚
明只是人不曾想到耳 吴因之曰所谓思若只向
卷三十四 第 45a 页 WYG0209-0732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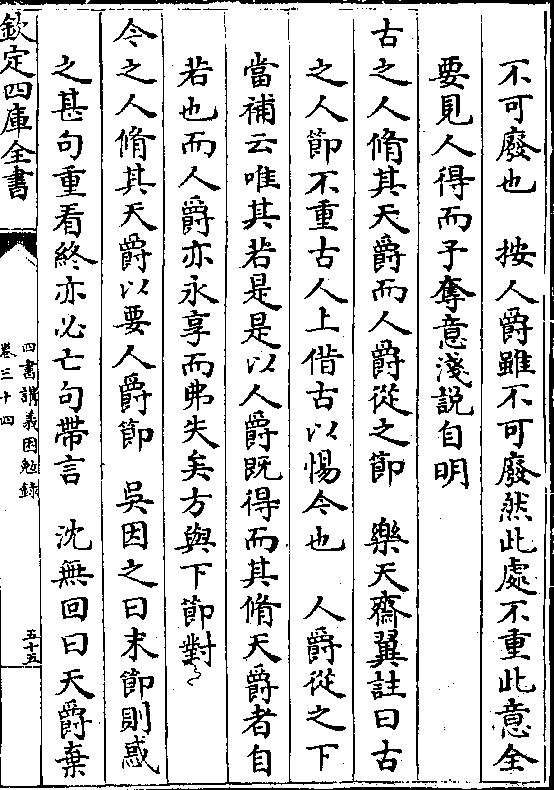 养处摸索也不济事须先从身上要看破盖人皆知
养处摸索也不济事须先从身上要看破盖人皆知血肉之躯之为身而不知此虽不可谓之非身又不
可即谓之身也乃人之真身必有在焉能思身之所
以为真然后能思养之所以为养若论其极则岂惟
小害大贱害贵为弗思彼老之长生犹为溺于养也
释之无生适以叛于养也溺于养者私其身不知此
身原非我所得私也叛于养者赘疣其身不知大冶
原未尝以我为赘疣也则亦未讲于慎思而已矣
人之于身也章总旨 吴因之曰通章重所以考其善
卷三十四 第 45b 页 WYG0209-0732d.png
 不善三句下只发明此意耳大人小人比对正见所
不善三句下只发明此意耳大人小人比对正见所养之善否而已当自审后独就养不善一边以垂鉴
戒盖申说养小之为小人而益见当审轻重于己也
乐天斋翼注曰首二节言养之善否决于己下深
戒不善养者而益以见其当自审也
人之于身也节 张彦陵曰人之于身也五句概论人
情 翼注曰身字浑融说勿露大体小体爱以心言
卷三十四 第 46a 页 WYG0209-0733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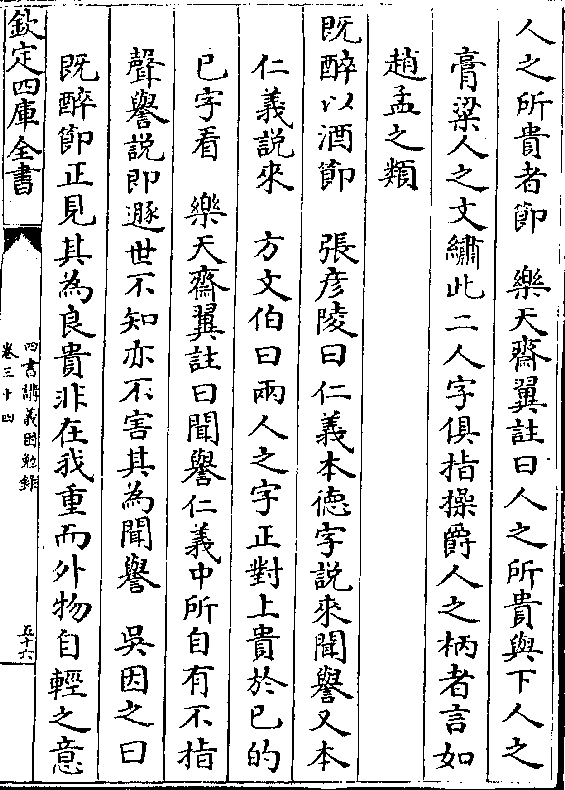 养以事言 乐天斋翼注曰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
养以事言 乐天斋翼注曰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必外身而他求哉己身之中轻重自别只就自己身
上反看一看则轻重审而善不善昭然于己取之是
示以稽考不眩的方法非谓近取而有馀也 盖此
是明其考之之法不是明其考之之易也 直解曰
于自己身上反而求之审其何者为重而在所当急
何者为轻而在所当缓养其所当重则善养其所当
轻则为不善善与不善特近取于吾身而自得其理
耳使非反之于己而审其轻重之伦有不失其养之
卷三十四 第 46b 页 WYG0209-0733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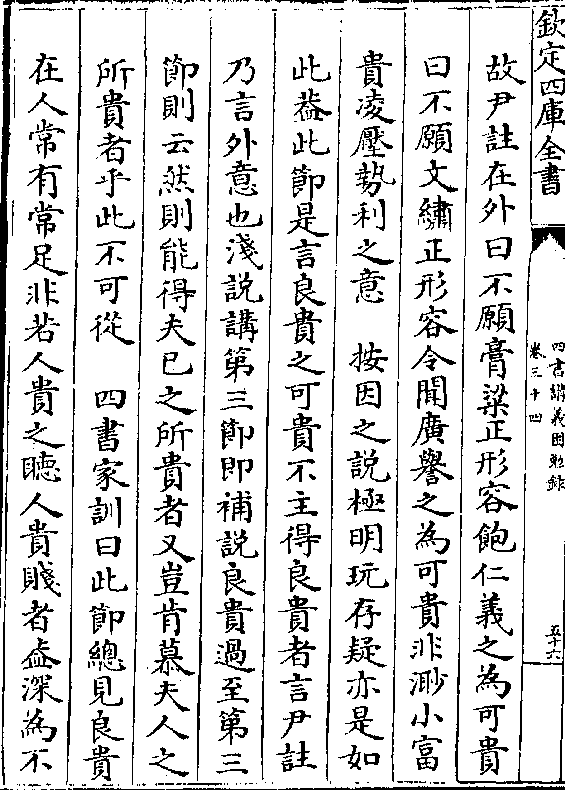 宜者哉
宜者哉体有贵贱节 吴因之曰过第二节当云何以见人当
取之于己以考其善不善耶 又曰体有贵贱二句
见体原有不同不是可概养的言体之在人非曰皆
贵而可养也盖有贵而亦有贱矣非曰皆大而可养
也盖有大而亦有小矣 张彦陵曰贵贱大小注虽
以口腹心志言看来还是虚虚说分称独尊为贵听
卷三十四 第 47a 页 WYG0209-0733c.png
 其役使为贱权无不统为大各分一官为小无以小
其役使为贱权无不统为大各分一官为小无以小二句见当审其轻重养其小二句正见其养之善不
善处 乐天斋翼注曰于为小人见养之不善于为
大人见养之善
今有埸师两节 张彦陵曰贱埸师曰狼疾人都著则
为二字见养小者为小人由己不能考其善不善耳
又曰一指肩背乃就小体中又分大小以喻不是
实语
饮食之人节 徐儆弦曰饮食不必言耽口腹之欲而
卷三十四 第 47b 页 WYG0209-0733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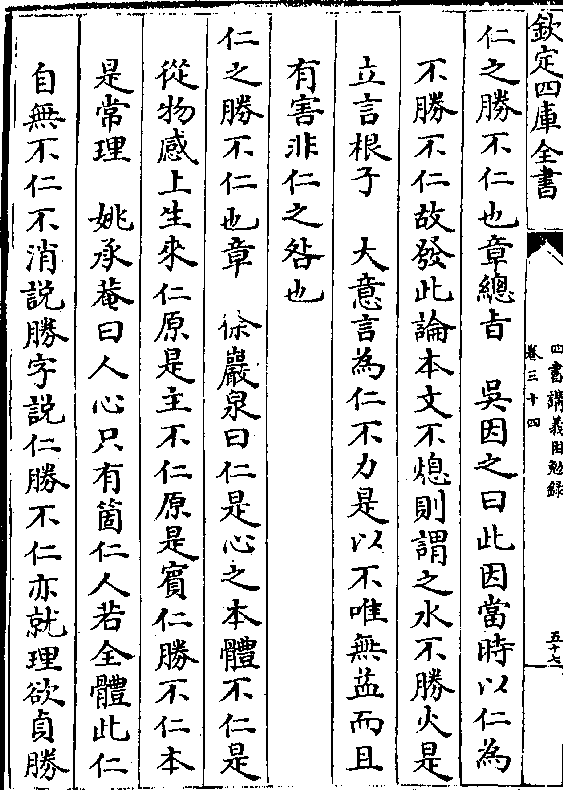 害心志之大只是不去照管自家本性理会自家身
害心志之大只是不去照管自家本性理会自家身子虽生于天地之间亦只养得一个口腹而已此所
以为饮食之人也庄子云风波之民孟子云饮食之
人一而已矣
饮食之人无有失也节 乐天斋翼注曰末节设言若
使养小而不失大则小体亦重何以养而取贱耶不
但为尺寸之肤只是言所系亦重是决言养小者之
卷三十四 第 48a 页 WYG0209-0734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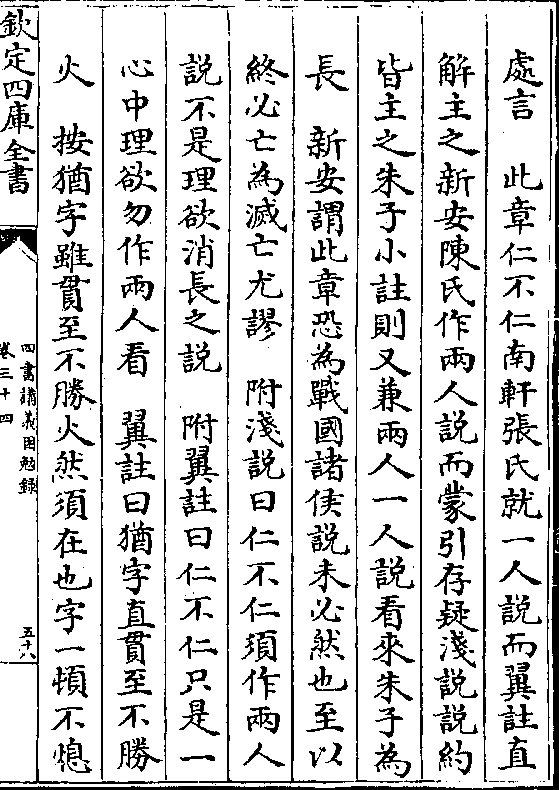 必失大耳 张觐文曰此非放宽饮食之人正吃紧
必失大耳 张觐文曰此非放宽饮食之人正吃紧唤醒饮食之人耳(文评) 末节依注是反言以决养小
者之必有失四书脉误附下 附四书脉曰无有失
是就饮食之人拨转他语若苟无害大害贵之失则
人心一转便是道心口腹之养即养心志岂仅仅为
尺寸之肤哉则字紧承无有失说非躯命所关之谓
此未尝不是但以此解口腹句则谬矣口腹句只
照注中躯命所关说 直解曰善养心志者只在辨
礼义而已能辨礼义则是嘑蹴不受至于万钟不取
卷三十四 第 48b 页 WYG0209-0734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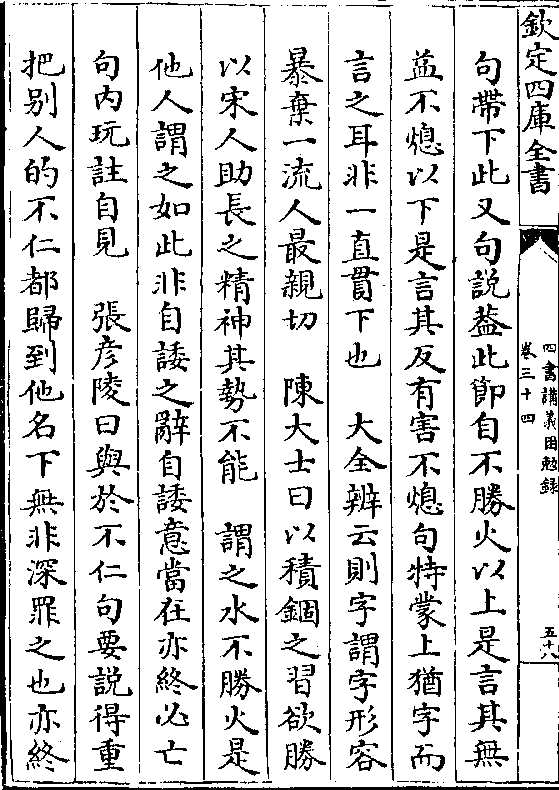 皆确然有一定之见而生死不能移利害不能易矣
皆确然有一定之见而生死不能移利害不能易矣钧是人也章总旨 张彦陵曰愚按此章纲领在从其
大体为大人一语而先立乎大四字是工夫下手处
思之一字则又指出个机窍正要人从形气中认出
主宰来则能参能赞的人即此能视能听的人莫大
品格其主张端的在自己心上 吴因之曰思之一
字是此章大关键又曰细玩此章便是非礼勿视听
卷三十四 第 49a 页 WYG0209-0734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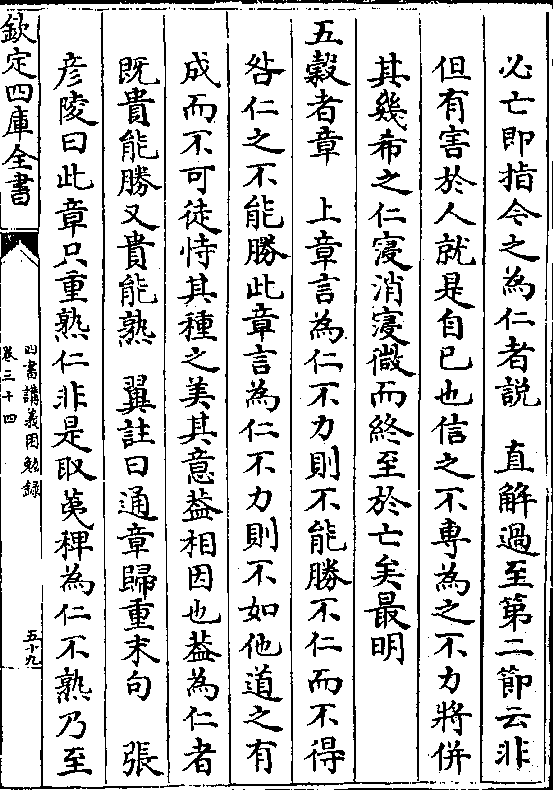 道理
道理钧是人也节 翼注曰前云钧是人也宜其成就同也
后云钧是人也宜其趋向同也意各有别为大人为
小人为字作谓字看不著力 四书镜曰大体小体
且空讲慢露出心与耳目为是 四书家训曰从与
养不同养以用功言从打养来以成功言
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节 吴因之曰从其大体只在
小者不能夺上但非先立其大则亦不能故特推明
而言之 又曰耳目之官节耳目一些主张也没有
卷三十四 第 49b 页 WYG0209-0734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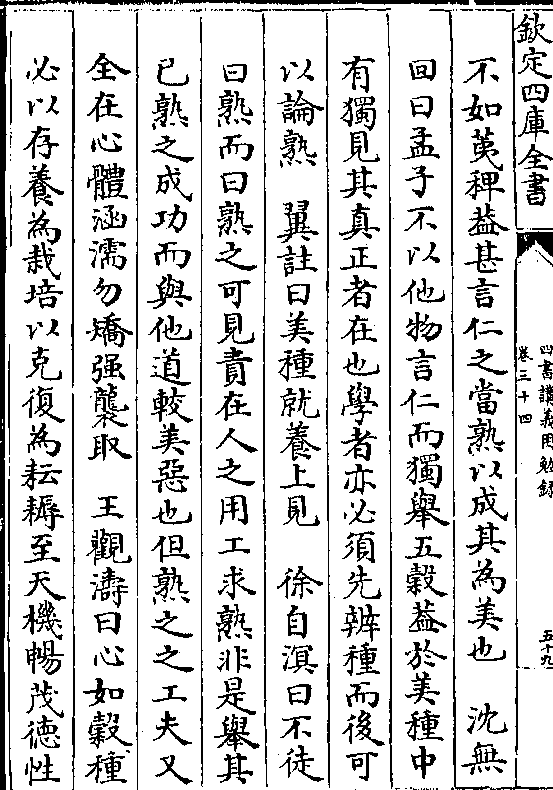 唯心做得主天之所与本有大小如此故人能先立
唯心做得主天之所与本有大小如此故人能先立乎其大主张耳目便称大人了思则得不思则不得
不是言其所关之大言唯其所主张也正反上蔽于
物意 乐天斋翼注曰自耳目至不得也二段只就
耳目与心上閒閒说不著人言不思不是人不肯思
思不是人用力去思乃是耳目与心小大之本体原
是如此 陈大士曰从大体而即以为大人从小体
卷三十四 第 50a 页 WYG0209-0735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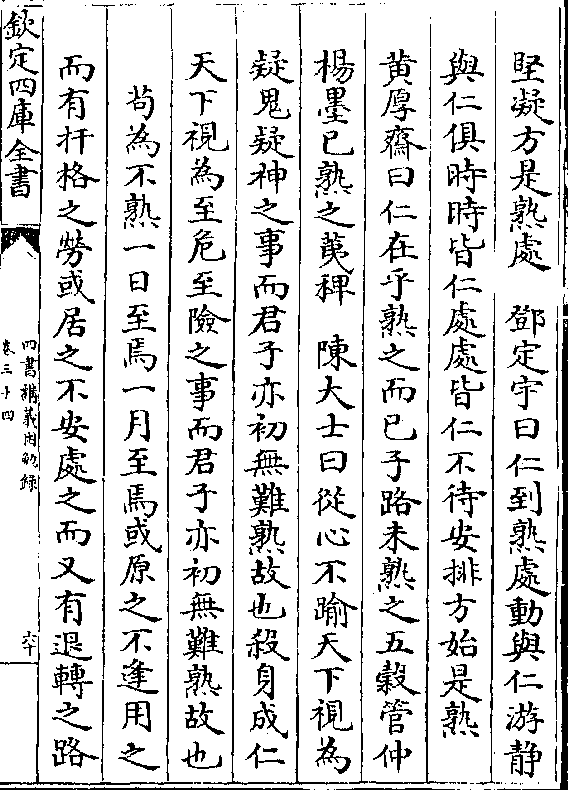 而即以为小人则大体之当从小体之不当从此不
而即以为小人则大体之当从小体之不当从此不待知者而决也然亦有欲从大体不从小体而卒不
如其愿者何也则以不得其从之之术也今夫小体
之不足恃也明矣所恃者独在能思之心使弃焉而
不立立焉而不先俱非所谓从之之术也何也不立
则我必不能以虚应不先立则我必不能以卒持故
夫古之君子知言养气积其不动之学问于恒居之
时而思患预防定其不惊之精神于涉境之际由是
可以交物而无所防此从乎大体之方而适于大人
卷三十四 第 50b 页 WYG0209-0735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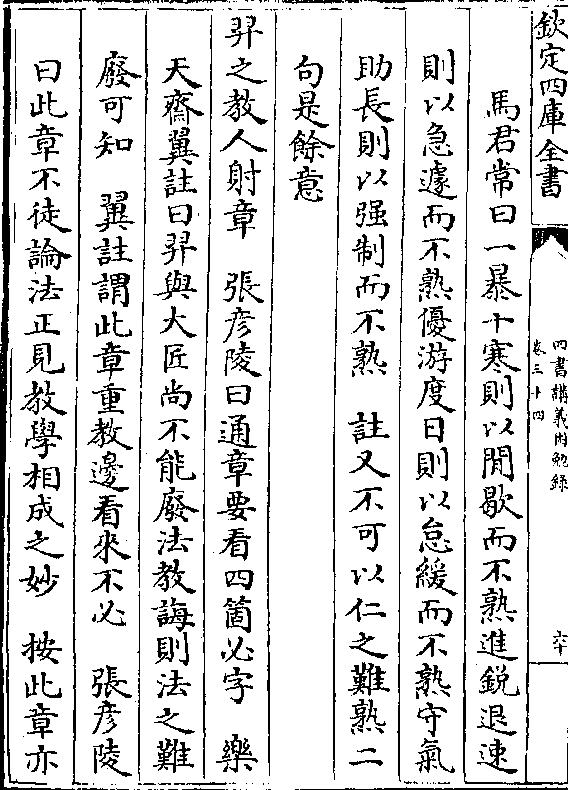 之路乎 四书脉曰蔽与引不同亦无甚先后盖为
之路乎 四书脉曰蔽与引不同亦无甚先后盖为奸声乱色所遮蔽便从他去矣 张彦陵曰引之而
去是引耳使听引目使视不是引心 陈伯玉曰思
则得之二句正形容思之灵通所以为大体与操则
存舍则亡有辨 吴因之曰若作次节文当云耳目
不思而蔽最易引物而为心之累而心官能思独操
得失之权则固可以制耳目者也使于天所与之中
卷三十四 第 51a 页 WYG0209-0735c.png
 有所独主而先立其大焉则所谓小者自不能夺矣
有所独主而先立其大焉则所谓小者自不能夺矣罗整庵困知记云圣人所谓无意无私意耳所谓
何思何虑以晓夫憧憧往来者书曰思曰睿睿作圣
非思则作圣何由故大学之教不曰无意惟曰诚意
中庸之训不曰无思惟曰慎思此吾儒入道之门穷
理尽性必由于此彼禅学者惟以顿悟为主必欲扫
除意见屏绝思虑将四面八方路头一齐塞住使其
心更无一线可通牢关固闭以冀其一旦忽然有省
终有所见不过灵觉之光景而已 张彦陵曰此天
卷三十四 第 51b 页 WYG0209-0735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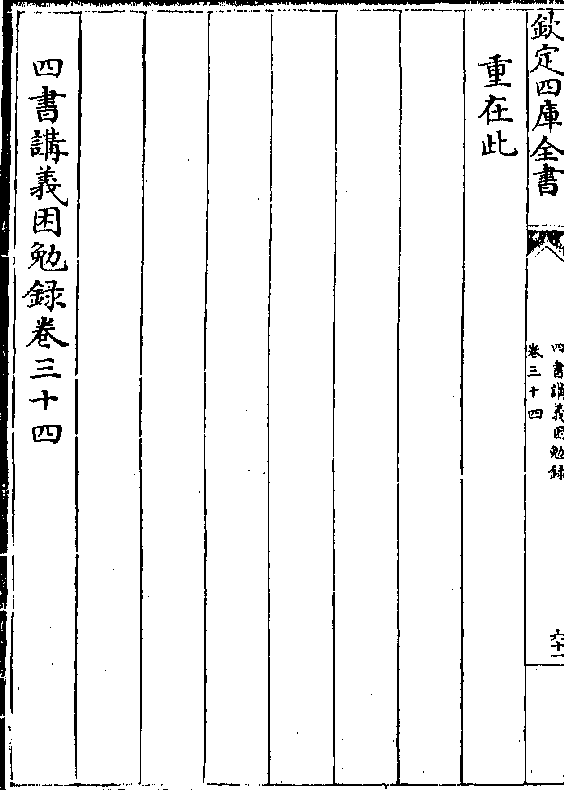 之所与我者总承上说要见天方赋予之初原是以
之所与我者总承上说要见天方赋予之初原是以心为耳目之主耳目不得不从心本一定不易者故
能先立其大即小者自不能夺只闲闲举个见成的
说 翼注曰立字有植立不仆之意谓之先立须在
声色未交之时与方交之始先有主张此亦不是矜
持把捉只是天理自强不息夺是夺心不但淫声邪
色即如目看诗书若心无正解亦是目夺其心推类
卷三十四 第 52a 页 WYG0209-0736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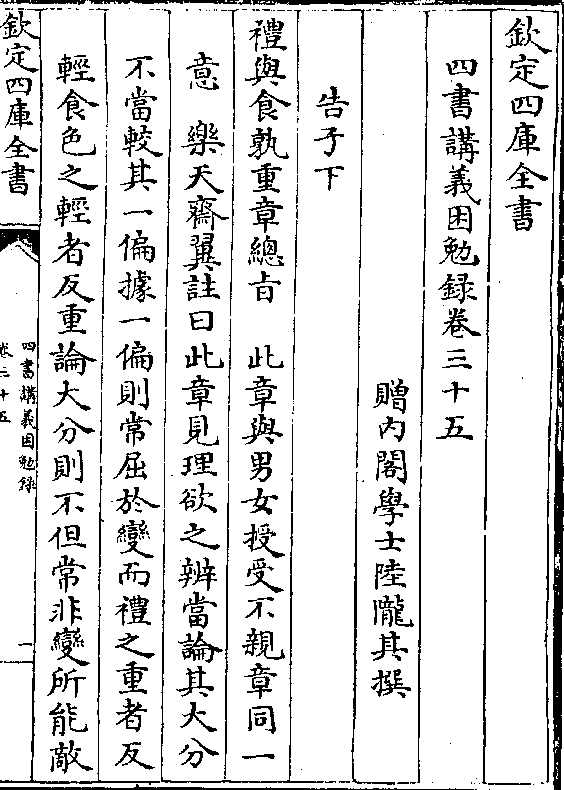 可见 庚戌林麟焻曰心立于耳目不交之地思固
可见 庚戌林麟焻曰心立于耳目不交之地思固以却物而见其能先心立于耳目方交之时思又以
御物而见其能先 此即翼注之意 先立似即中
庸前定之意不必专就不睹闻与隐微时说也翼注
说须善看徐自溟说殊有见 徐自溟曰人生终日
开目便视触耳便听又何处去先立若必在静坐时
先立定此心然后去视去听决无此理只是将此心
念念操持时时提醒使能思之体常足为应用之主
不待物已交之后才来用此心去思也 崔后渠曰
卷三十四 第 52b 页 WYG0209-0736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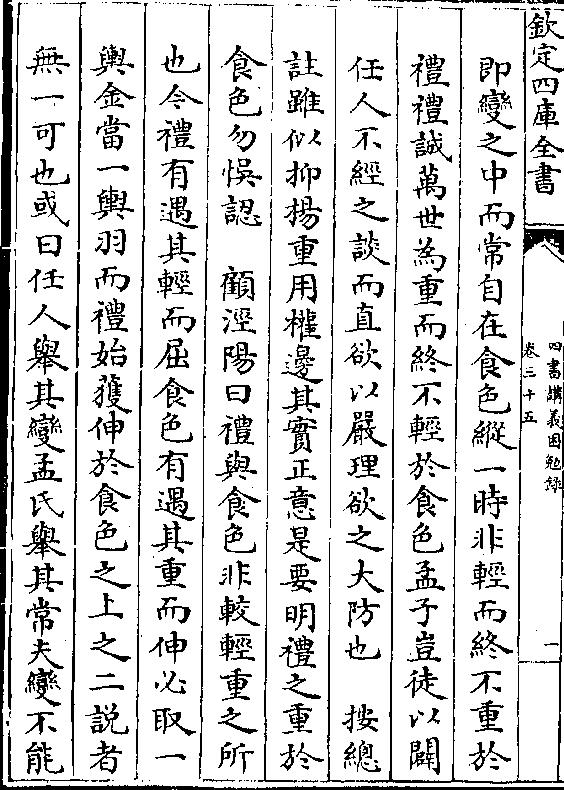 先立乎其大者能思之谓也夫耳目有用而无思故
先立乎其大者能思之谓也夫耳目有用而无思故邪正兼收心则能思以制用故取舍不忒心不思则
役于物犹耳目也何立之有故外思而言立非告子
之强制则释氏之悟空 直解曰立本固可以应事
而制外亦所以养中故必于淫声美色禁之使不接
于耳目庶几外者不入而内者亦固矣此又内外交
脩之道 按直解所说即所谓无暴其气也亦是先
卷三十四 第 53a 页 WYG0209-0736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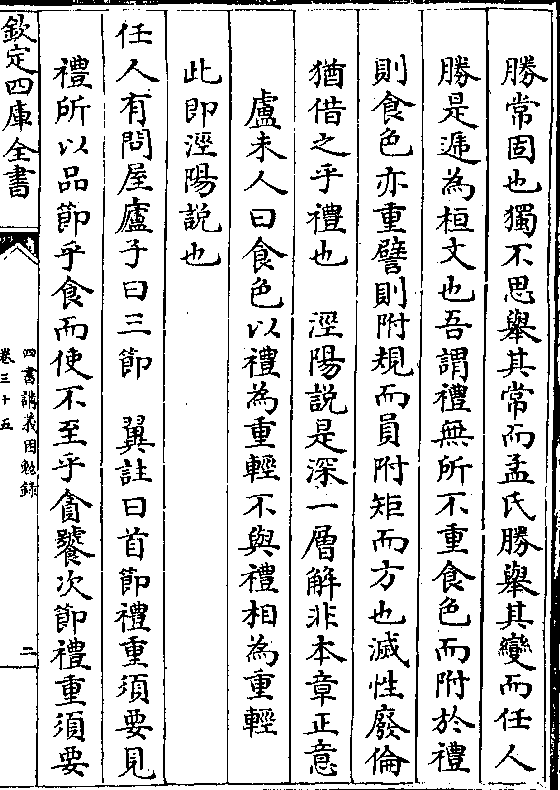 立乎大之工夫不必在言外见也盖持志养气皆所
立乎大之工夫不必在言外见也盖持志养气皆所以从乎大体不持志不养气则皆所以从乎小体时
文有云任耳目而忘心而心遂化而为耳目因心以
及耳目而耳目亦可进而见心正得此意 嘉靖壬
午福建程讲先立乎大云制之于动则难矣必主敬
于无声之先慎之于动亦晚矣必存诚于不睹之始
此亦近直解之说 张彦陵曰到小者不能夺固是
妙其能思之用亦只是还其无思之体 乐天斋翼
注曰此谓大人句顶上二句言此所谓从其大体者
卷三十四 第 53b 页 WYG0209-0736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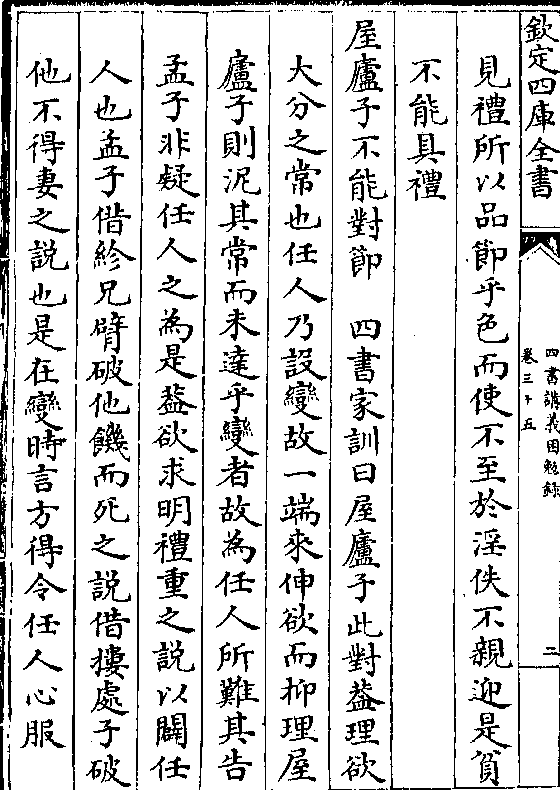 而安得不为大人乎 堪舆二字蒙引一说谓堪者
而安得不为大人乎 堪舆二字蒙引一说谓堪者天道舆者地道又一说谓堪任也只是谓任载之舆
指人在地之上而言在地之上则在天之下矣二说
未知孰是且堪舆二字亦未知出于何书
有天爵者章总旨 张彦陵曰愚按此章借爵之一字
以分别天人正欲人转人爵之慕而为天爵之脩也
曰惑之甚曰终亦必亡都是点醒世人语 冯开之
卷三十四 第 54a 页 WYG0209-0737a.png
 曰古之时天人之爵合今之时天人之爵分如此说
曰古之时天人之爵合今之时天人之爵分如此说方明 张彦陵曰学术之淳漓事功之真假世运之
升降皆出于此 庚戌会墨左襄南独从正学术维
世道勘出孟夫子立言警世本心最见其大
有天爵者节 钟乾所曰天爵之说孟子创之实得自
维皇宠锡语意来 浅说谓天爵不必说是天与者
似不是 翼注曰人性之德莫大乎仁义而忠信即
仁义之有实处至于乐此仁义忠信之善而不倦只
是秉彝好德自然之情切勿涉工夫故曰自然之贵
卷三十四 第 54b 页 WYG0209-0737b.png

乐善不倦翼注谓勿涉工夫极是蒙引以美大圣
神及乐斯二者来说者乃比例之辞非正解也双峰
谓仁义人人有之忠信乐善人所当勉则误矣若浅
说讲脩其天爵而曰尽夫仁义忠信之理造于乐善
不倦之地便不妨盖论本体则乐善不倦本来如此
论工夫则乐善不倦乃造其极之境也 附刘上玉
曰首节正说不必遽侧贬人爵人爵亦御世之大分
卷三十四 第 55a 页 WYG0209-0737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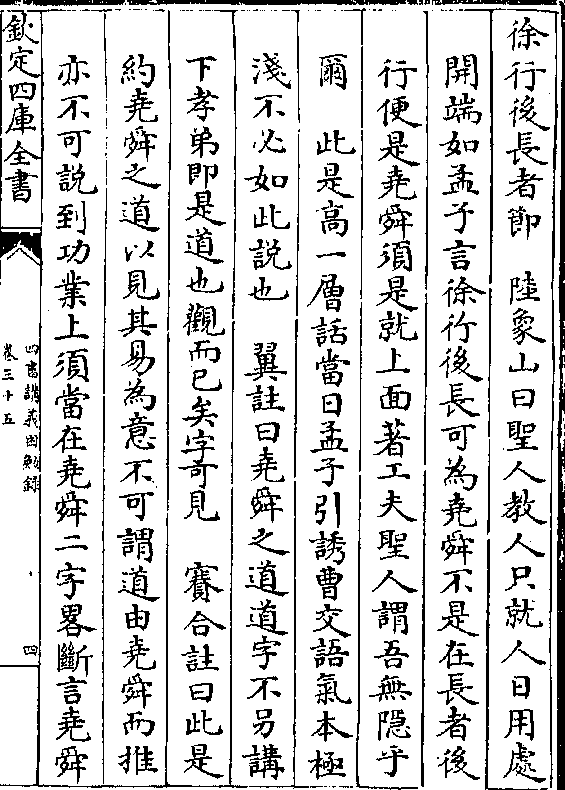 不可废也 按人爵虽不可废然此处不重此意全
不可废也 按人爵虽不可废然此处不重此意全要见人得而予夺意浅说自明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从之节 乐天斋翼注曰古
之人节不重古人上借古以惕今也 人爵从之下
当补云唯其若是是以人爵既得而其脩天爵者自
若也而人爵亦永享而弗失矣方与下节对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节 吴因之曰末节则惑
之甚句重看终亦必亡句带言 沈无回曰天爵弃
而人爵亡即为要人爵者计亦不当一日不脩天爵
卷三十四 第 55b 页 WYG0209-0737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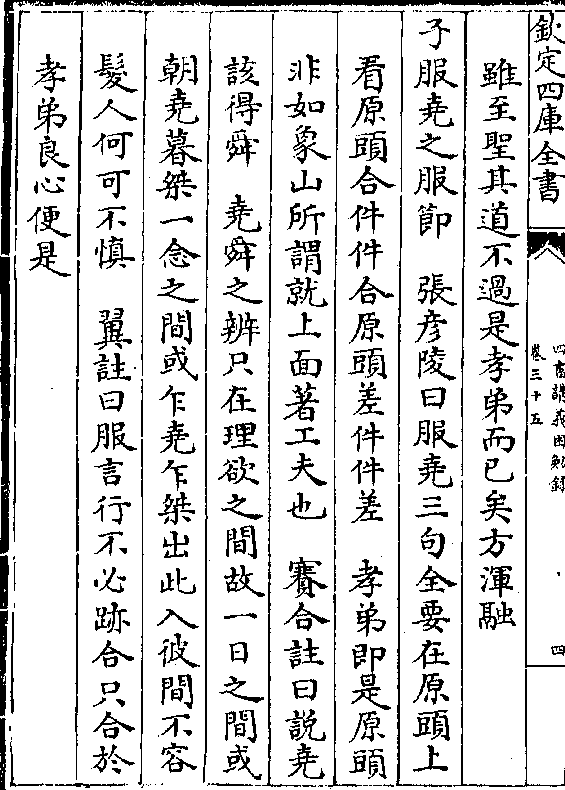 此孟子不得已唤醒人之辞湛甘泉曰其要之心即
此孟子不得已唤醒人之辞湛甘泉曰其要之心即其弃之之心也
欲贵者节 张彦陵曰蔡虚斋云贵因有所崇重而得
名欲贵只虚虚说个愿慕尊荣意 按蒙引并无此
说浅说亦主爵位言 湖南讲曰欲贵即欲人爵的
贵 乐天斋翼注曰贵于己就是良贵弗思耳非慨
人不思正唤人去思耳要得儆醒人意
卷三十四 第 56a 页 WYG0209-0738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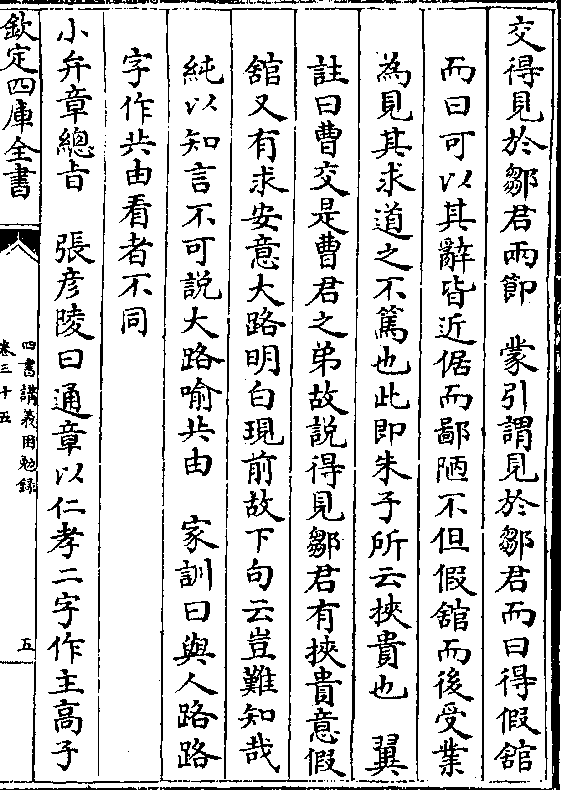 人之所贵者节 乐天斋翼注曰人之所贵与下人之
人之所贵者节 乐天斋翼注曰人之所贵与下人之膏梁人之文绣此二人字俱指操爵人之柄者言如
赵孟之类
既醉以酒节 张彦陵曰仁义本德字说来闻誉又本
仁义说来 方文伯曰两人之字正对上贵于己的
己字看 乐天斋翼注曰闻誉仁义中所自有不指
声誉说即遁世不知亦不害其为闻誉 吴因之曰
既醉节正见其为良贵非在我重而外物自轻之意
故尹注在外曰不愿膏粱正形容饱仁义之为可贵
卷三十四 第 56b 页 WYG0209-0738b.png
 曰不愿文绣正形容令闻广誉之为可贵非渺小富
曰不愿文绣正形容令闻广誉之为可贵非渺小富贵凌压势利之意 按因之说极明玩存疑亦是如
此盖此节是言良贵之可贵不主得良贵者言尹注
乃言外意也浅说讲第三节即补说良贵过至第三
节则云然则能得夫己之所贵者又岂肯慕夫人之
所贵者乎此不可从 四书家训曰此节总见良贵
在人常有常足非若人贵之听人贵贱者盖深为不
卷三十四 第 57a 页 WYG0209-0738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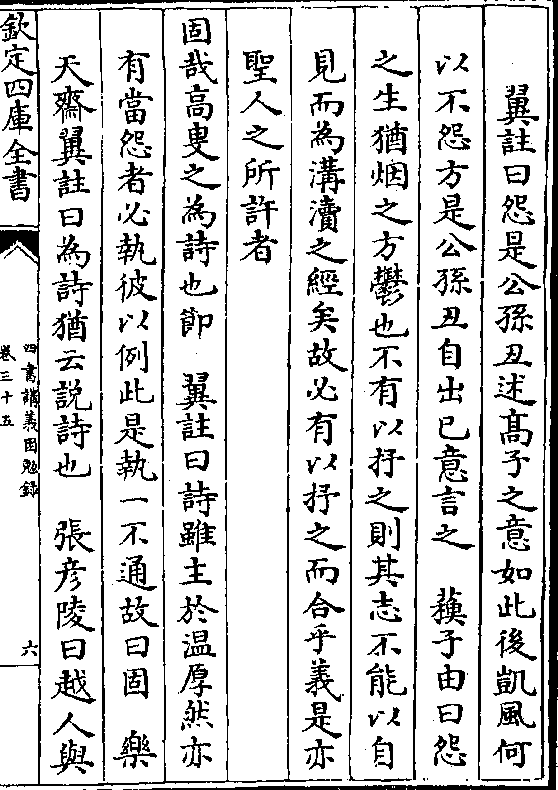 思者醒也 按此与因之存疑合 玩因之说则知
思者醒也 按此与因之存疑合 玩因之说则知新安陈氏云两不愿即中庸不愿乎外之意亦是言
其大意如此非正解本文也中庸所谓不愿乃是主
得良贵者说云峰一条亦与新安一例 四书脉曰
在我者取不尽用不竭淡泊固足明志而纷华亦非
夺心不必膏绣亦不必不膏绣孔之曲肱舜之袗衣
同一不愿而已 此说得最妙蒙引谓不愿是无慕
于彼非不愿就也其意亦如此
仁之胜不仁也章总旨 吴因之曰此因当时以仁为
卷三十四 第 57b 页 WYG0209-0738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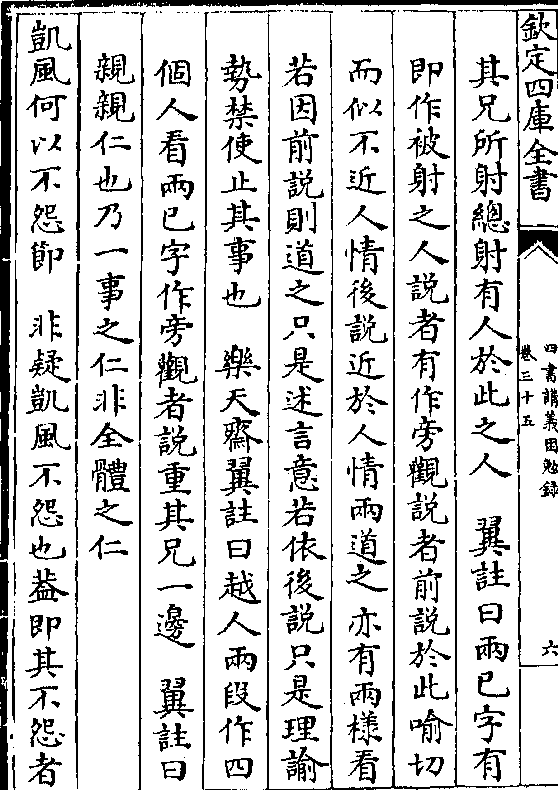 不胜不仁故发此论本文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是
不胜不仁故发此论本文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是立言根子 大意言为仁不力是以不唯无益而且
有害非仁之咎也
仁之胜不仁也章 徐岩泉曰仁是心之本体不仁是
从物感上生来仁原是主不仁原是宾仁胜不仁本
是常理 姚承庵曰人心只有个仁人若全体此仁
自无不仁不消说胜字说仁胜不仁亦就理欲贞胜
卷三十四 第 58a 页 WYG0209-0739a.png
 处言 此章仁不仁南轩张氏就一人说而翼注直
处言 此章仁不仁南轩张氏就一人说而翼注直解主之新安陈氏作两人说而蒙引存疑浅说说约
皆主之朱子小注则又兼两人一人说看来朱子为
长 新安谓此章恐为战国诸侯说未必然也至以
终必亡为灭亡尤谬 附浅说曰仁不仁须作两人
说不是理欲消长之说 附翼注曰仁不仁只是一
心中理欲勿作两人看 翼注曰犹字直贯至不胜
火 按犹字虽贯至不胜火然须在也字一顿不熄
句带下此又句说盖此节自不胜火以上是言其无
卷三十四 第 58b 页 WYG0209-0739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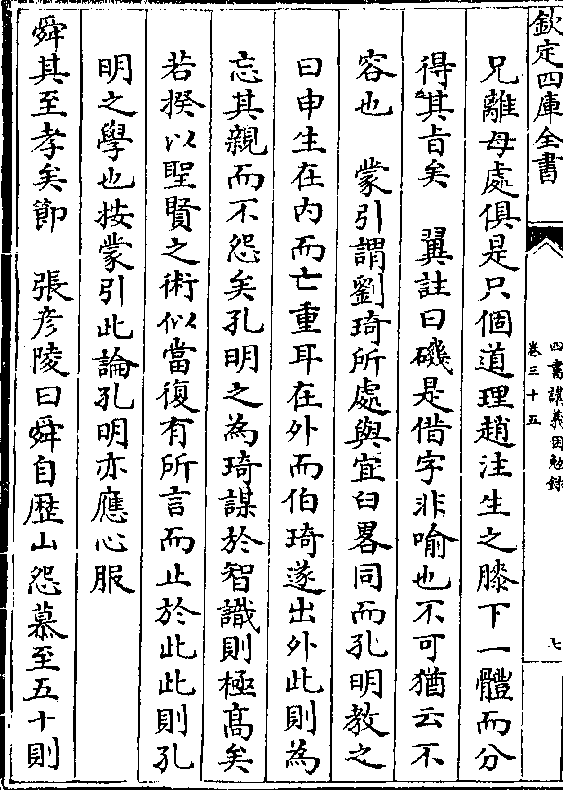 益不熄以下是言其反有害不熄句特蒙上犹字而
益不熄以下是言其反有害不熄句特蒙上犹字而言之耳非一直贯下也 大全辨云则字谓字形容
暴弃一流人最亲切 陈大士曰以积锢之习欲胜
以宋人助长之精神其势不能 谓之水不胜火是
他人谓之如此非自诿之辞自诿意当在亦终必亡
句内玩注自见 张彦陵曰与于不仁句要说得重
把别人的不仁都归到他名下无非深罪之也亦终
卷三十四 第 59a 页 WYG0209-0739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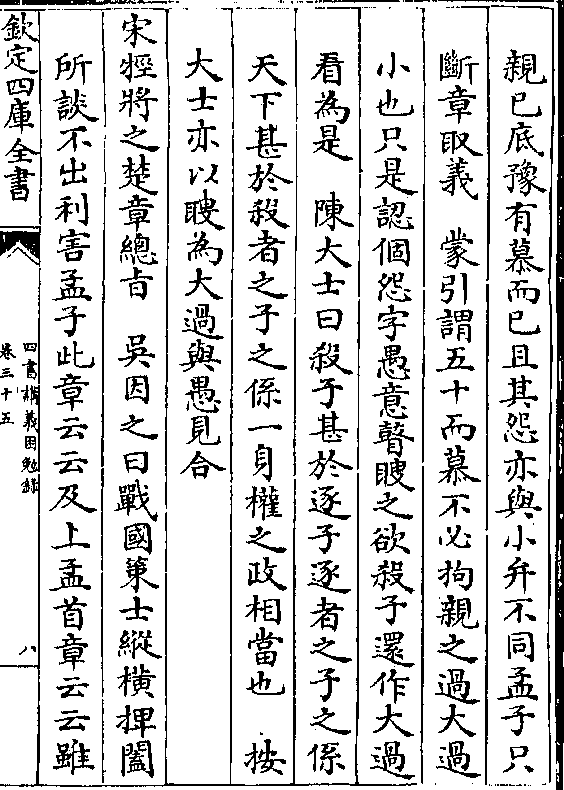 必亡即指今之为仁者说 直解过至第二节云非
必亡即指今之为仁者说 直解过至第二节云非但有害于人就是自己也信之不专为之不力将并
其几希之仁寖消寖微而终至于亡矣最明
五谷者章 上章言为仁不力则不能胜不仁而不得
咎仁之不能胜此章言为仁不力则不如他道之有
成而不可徒恃其种之美其意盖相因也盖为仁者
既贵能胜又贵能熟 翼注曰通章归重末句 张
彦陵曰此章只重熟仁非是取荑稗为仁不熟乃至
不如荑稗盖甚言仁之当熟以成其为美也 沈无
卷三十四 第 59b 页 WYG0209-0739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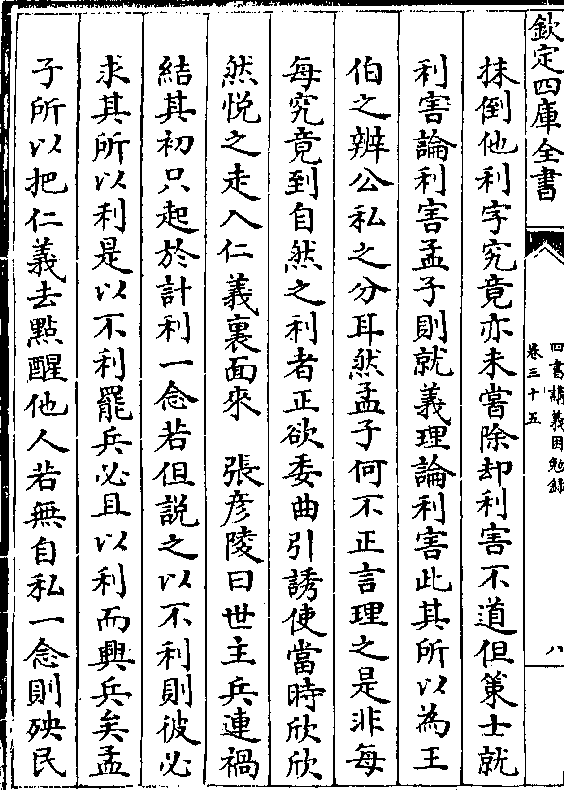 回曰孟子不以他物言仁而独举五谷盖于美种中
回曰孟子不以他物言仁而独举五谷盖于美种中有独见其真正者在也学者亦必须先辨种而后可
以论熟 翼注曰美种就养上见 徐自溟曰不徒
曰熟而曰熟之可见责在人之用工求熟非是举其
已熟之成功而与他道较美恶也但熟之之工夫又
全在心体涵濡勿矫强袭取 王观涛曰心如谷种
必以存养为栽培以克复为耘耨至天机畅茂德性
卷三十四 第 60a 页 WYG0209-0740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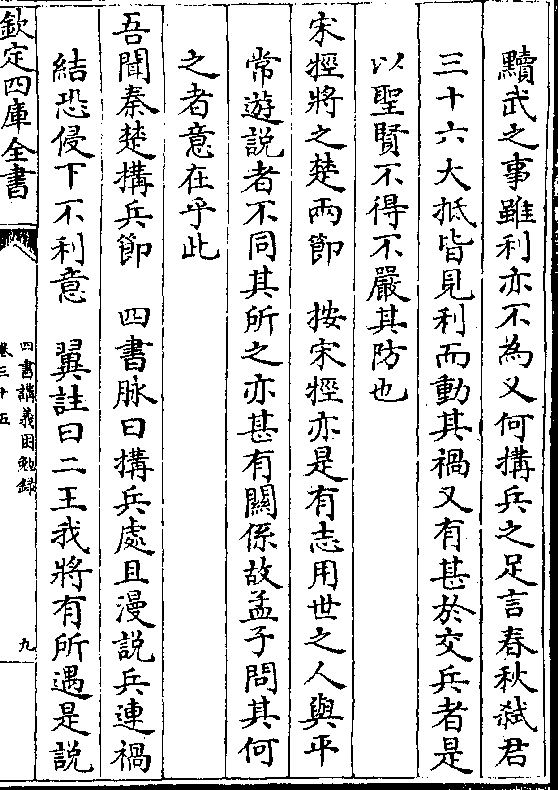 坚凝方是熟处 邓定宇曰仁到熟处动与仁游静
坚凝方是熟处 邓定宇曰仁到熟处动与仁游静与仁俱时时皆仁处处皆仁不待安排方始是熟
黄厚斋曰仁在乎熟之而已子路未熟之五谷管仲
杨墨已熟之荑稗 陈大士曰从心不踰天下视为
疑鬼疑神之事而君子亦初无难熟故也杀身成仁
天下视为至危至险之事而君子亦初无难熟故也
苟为不熟一日至焉一月至焉或原之不逢用之
而有捍格之劳或居之不安处之而又有退转之路
卷三十四 第 60b 页 WYG0209-0740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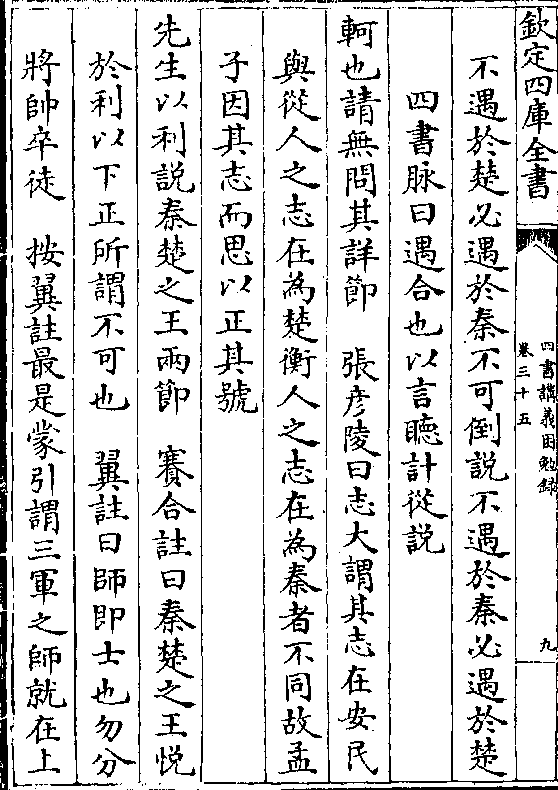 马君常曰一暴十寒则以閒歇而不熟进锐退速
马君常曰一暴十寒则以閒歇而不熟进锐退速则以急遽而不熟优游度日则以怠缓而不熟守气
助长则以强制而不熟 注又不可以仁之难熟二
句是馀意
羿之教人射章 张彦陵曰通章要看四个必字 乐
天斋翼注曰羿与大匠尚不能废法教诲则法之难
废可知 翼注谓此章重教边看来不必 张彦陵
曰此章不徒论法正见教学相成之妙 按此章亦
卷三十四 第 61a 页 WYG0209-0740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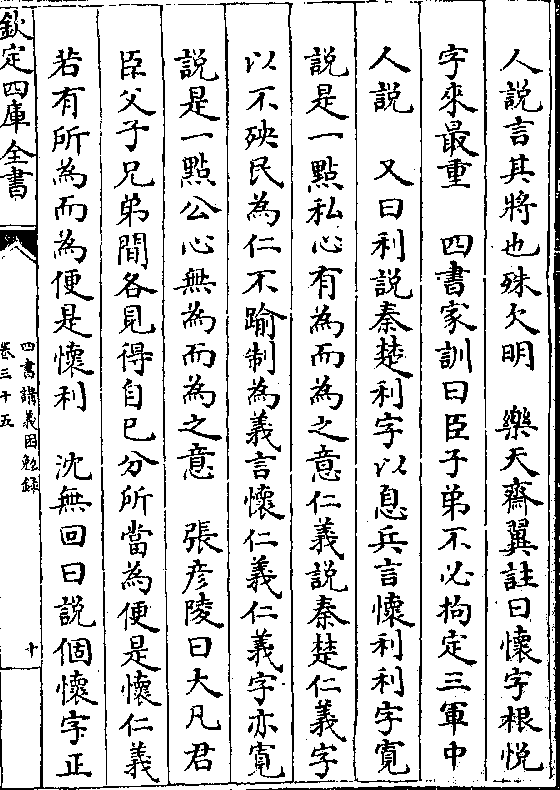 无此意 徐儆弦曰执规矩以尽匠之神亦非上达
无此意 徐儆弦曰执规矩以尽匠之神亦非上达之妙也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按此是梓匠章意
非此章意也 葛屺瞻曰正意不曾说破然前章论
性论心论仁而以此结之当是教人求仁与心性者
必遵个方法乃可坐进此道耳 乐天斋翼注曰二
志字二以字亦有别志即内志正之志引弓满彀凝
神不分乃可命中故曰志以用也规矩无一定之则
大小方员唯所用之故曰以 按虽有此分别然不
重在此
卷三十四 第 61b 页 WYG0209-0740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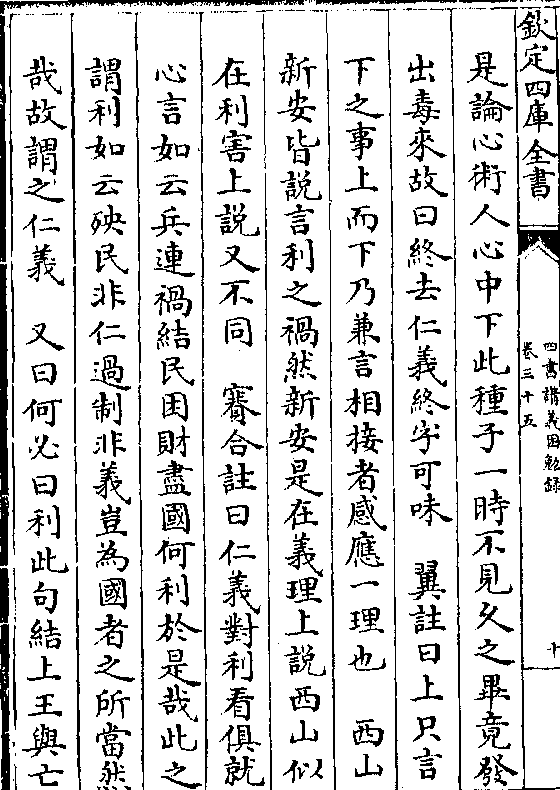 四书讲义困勉录卷三十四
四书讲义困勉录卷三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