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卷五 第 1a 页 WYG0204-0810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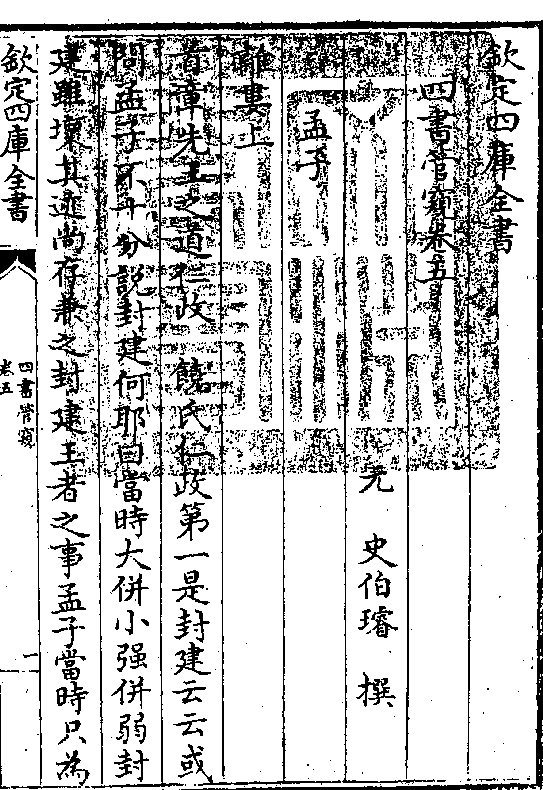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四书管窥卷五
元 史伯璿 撰
孟子
离娄上
首章先王之道仁政 饶氏仁政第一是封建云云或
问孟子不十分说封建何耶曰当时大并小强并弱封
建虽坏其迹尚存兼之封建王者之事孟子当时只为
卷五 第 1b 页 WYG0204-0810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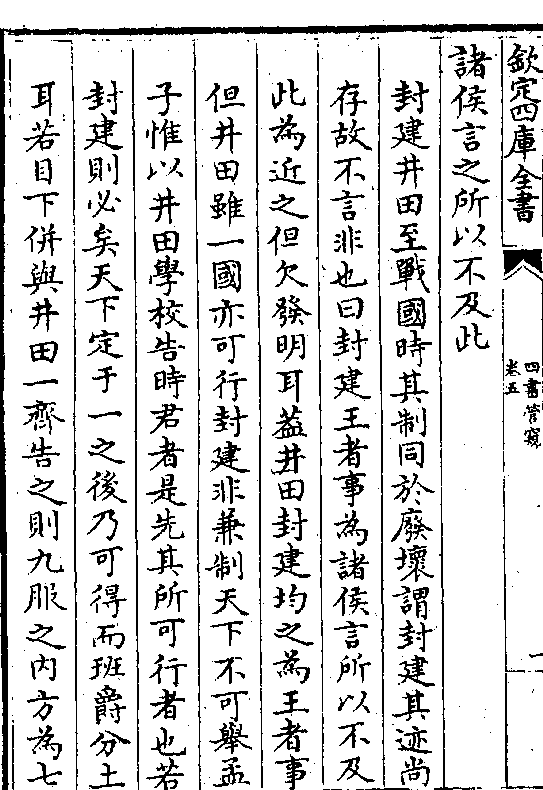 诸侯言之所以不及此
诸侯言之所以不及此封建井田至战国时其制同于废坏谓封建其迹尚
存故不言非也曰封建王者事为诸侯言所以不及
此为近之但欠𤼵明耳盖井田封建均之为王者事
但井田虽一国亦可行封建非兼制天下不可举孟
子惟以井田学校告时君者是先其所可行者也若
封建则必矣天下定于一之后乃可得而班爵分土
耳若目下并与井田一齐告之则九服之内方为七
卷五 第 2a 页 WYG0204-0811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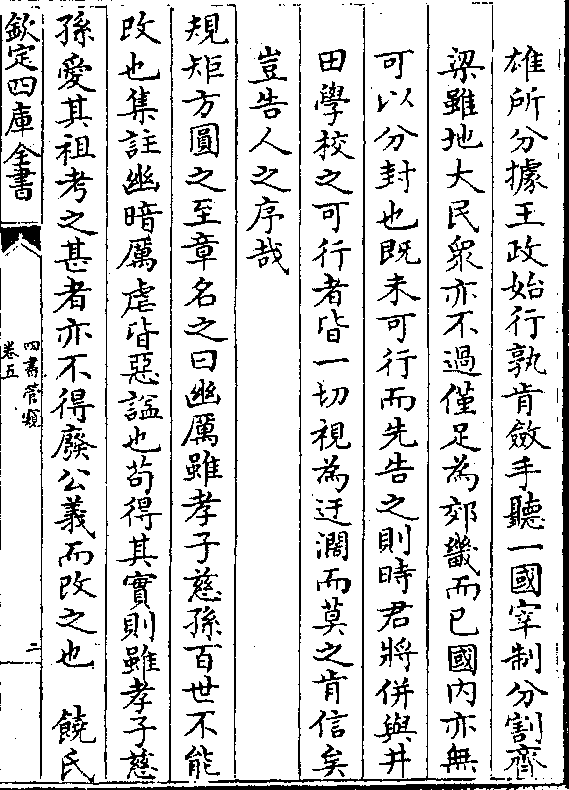 雄所分据王政始行孰肯敛手听一国宰制分割齐
雄所分据王政始行孰肯敛手听一国宰制分割齐梁虽地大民众亦不过仅足为郊畿而已国内亦无
可以分封也既未可行而先告之则时君将并与井
田学校之可行者皆一切视为迂阔而莫之肯信矣
岂告人之序哉
规矩方圆之至章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
改也集注幽暗厉虐皆恶谥也苟得其实则虽孝子慈
孙爱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废公义而改之也 饶氏
卷五 第 2b 页 WYG0204-0811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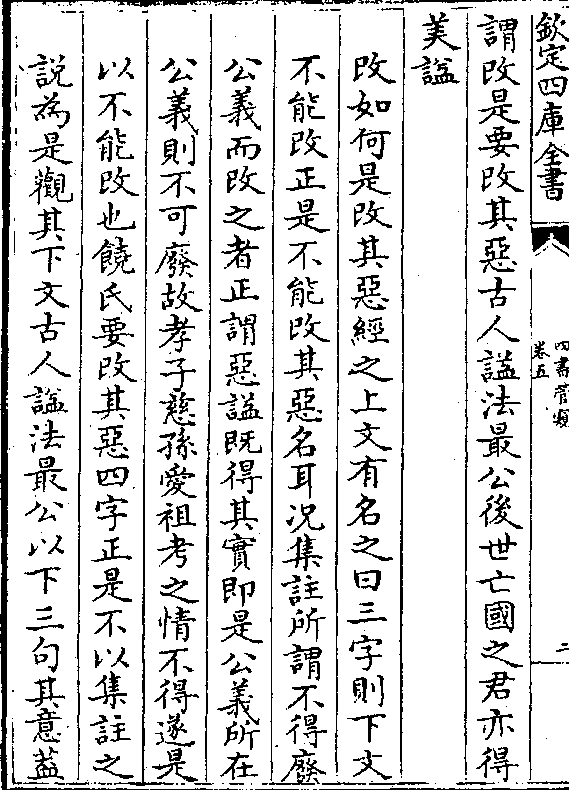 谓改是要改其恶古人谥法最公后世亡国之君亦得
谓改是要改其恶古人谥法最公后世亡国之君亦得美谥
改如何是改其恶经之上文有名之曰三字则下文
不能改正是不能改其恶名耳况集注所谓不得废
公义而改之者正谓恶谥既得其实即是公义所在
公义则不可废故孝子慈孙爱祖考之情不得遂是
以不能改也饶氏要改其恶四字正是不以集注之
说为是观其下文古人谥法最公以下三句其意盖
卷五 第 3a 页 WYG0204-0811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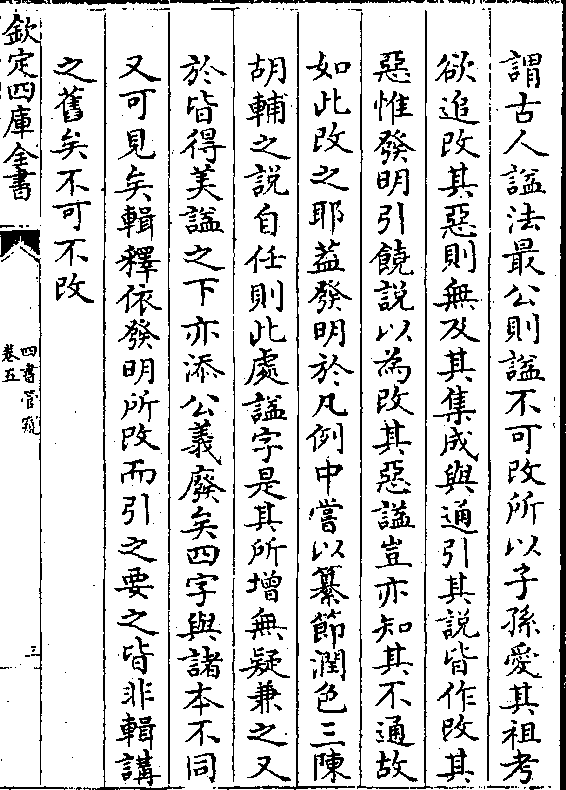 谓古人谥法最公则谥不可改所以子孙爱其祖考
谓古人谥法最公则谥不可改所以子孙爱其祖考欲追改其恶则无及其集成与通引其说皆作改其
恶惟𤼵明引饶说以为改其恶谥岂亦知其不通故
如此改之耶盖𤼵明于凡例中尝以纂节润色三陈
胡辅之说自任则此处谥字是其所增无疑兼之又
于皆得美谥之下亦添公义废矣四字与诸本不同
又可见矣辑释依𤼵明所改而引之要之皆非辑讲
之旧矣不可不改
卷五 第 3b 页 WYG0204-0811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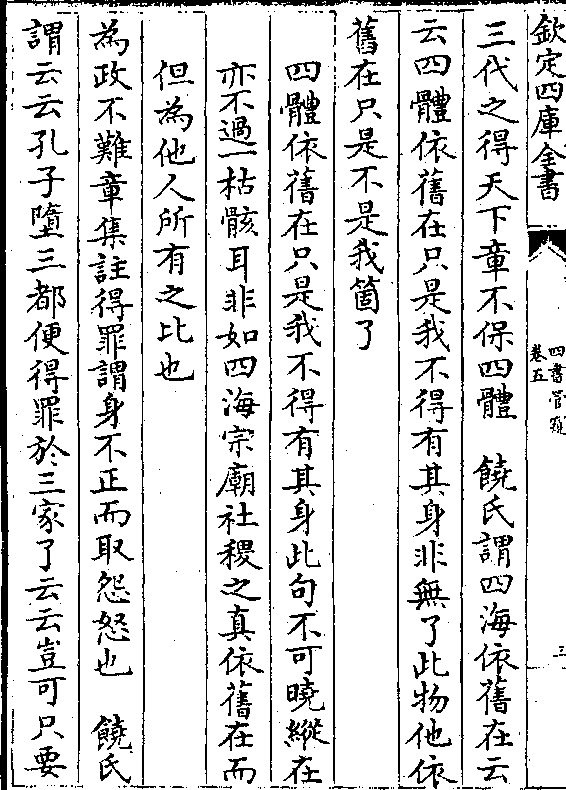 三代之得天下章不保四体 饶氏谓四海依旧在云
三代之得天下章不保四体 饶氏谓四海依旧在云云四体依旧在只是我不得有其身非无了此物他依
旧在只是不是我个了
四体依旧在只是我不得有其身此句不可晓纵在
亦不过一枯骸耳非如四海宗庙社稷之真依旧在而
但为他人所有之比也
为政不难章集注得罪谓身不正而取怨怒也 饶氏
谓云云孔子堕三都便得罪于三家了云云岂可只要
卷五 第 4a 页 WYG0204-0812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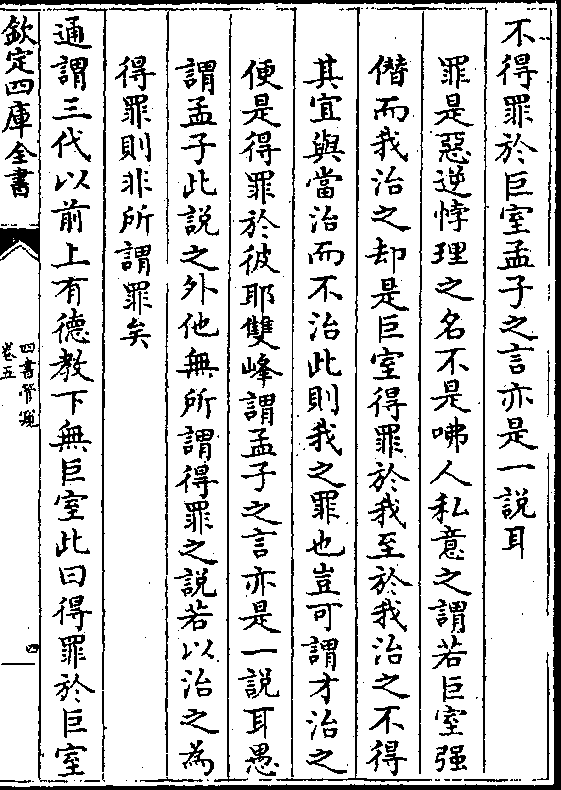 不得罪于巨室孟子之言亦是一说耳
不得罪于巨室孟子之言亦是一说耳罪是恶逆悖理之名不是咈人私意之谓若巨室强
僣而我治之却是巨室得罪于我至于我治之不得
其宜与当治而不治此则我之罪也岂可谓才治之
便是得罪于彼耶双峰谓孟子之言亦是一说耳愚
谓孟子此说之外他无所谓得罪之说若以治之为
得罪则非所谓罪矣
通谓三代以前上有德教下无巨室此曰得罪于巨室
卷五 第 4b 页 WYG0204-0812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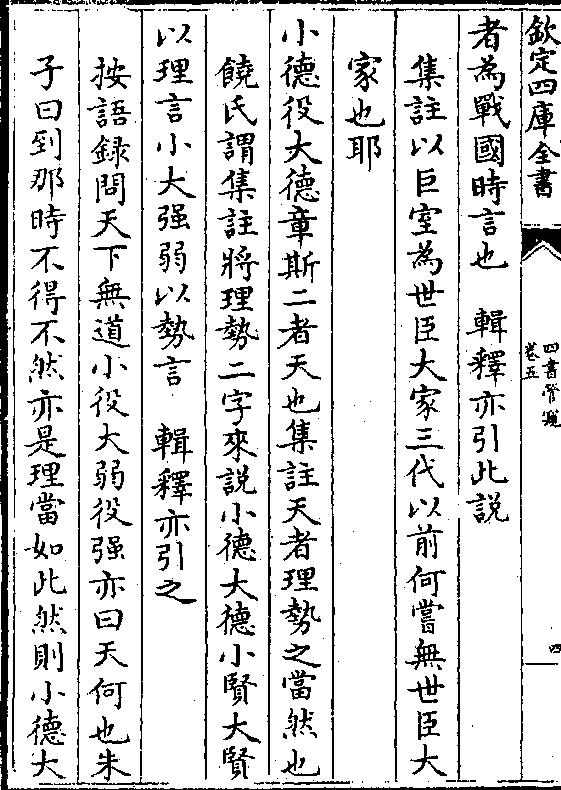 者为战国时言也 辑释亦引此说
者为战国时言也 辑释亦引此说集注以巨室为世臣大家三代以前何尝无世臣大
家也耶
小德役大德章斯二者天也集注天者理势之当然也
饶氏谓集注将理势二字来说小德大德小贤大贤
以理言小大强弱以势言 辑释亦引之
按语录问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亦曰天何也朱
子曰到那时不得不然亦是理当如此然则小德大
卷五 第 5a 页 WYG0204-0812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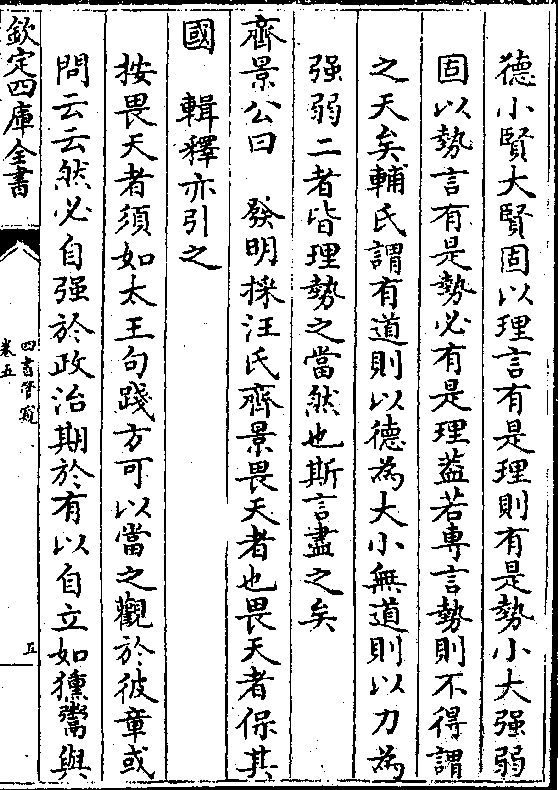 德小贤大贤固以理言有是理则有是势小大强弱
德小贤大贤固以理言有是理则有是势小大强弱固以势言有是势必有是理盖若专言势则不得谓
之天矣辅氏谓有道则以德为大小无道则以力为
强弱二者皆理势之当然也斯言尽之矣
齐景公曰 𤼵明采汪氏齐景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
国 辑释亦引之
按畏天者须如太王句践方可以当之观于彼章或
问云云然必自强于政治期于有以自立如獯鬻与
卷五 第 5b 页 WYG0204-0812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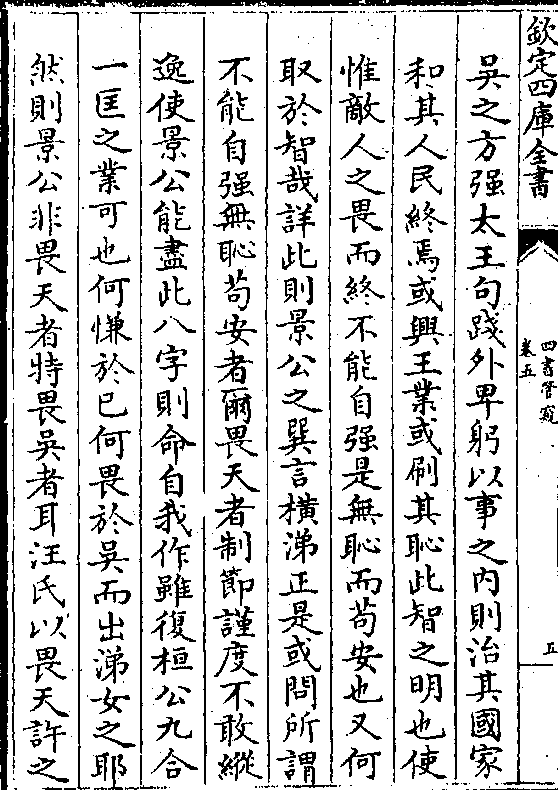 吴之方强太王句践外卑躬以事之内则治其国家
吴之方强太王句践外卑躬以事之内则治其国家和其人民终焉或兴王业或刷其耻此智之明也使
惟敌人之畏而终不能自强是无耻而苟安也又何
取于智哉详此则景公之巽言横涕正是或问所谓
不能自强无耻苟安者尔畏天者制节谨度不敢纵
逸使景公能尽此八字则命自我作虽复桓公九合
一匡之业可也何慊于己何畏于吴而出涕女之耶
然则景公非畏天者特畏吴者耳汪氏以畏天许之
卷五 第 6a 页 WYG0204-0813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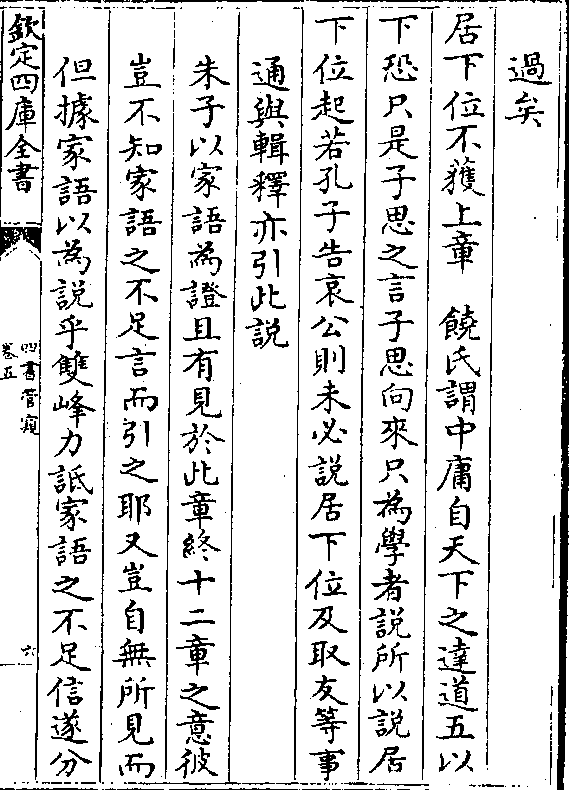 过矣
过矣居下位不获上章 饶氏谓中庸自天下之达道五以
下恐只是子思之言子思向来只为学者说所以说居
下位起若孔子告哀公则未必说居下位及取友等事
通与辑释亦引此说
朱子以家语为證且有见于此章终十二章之意彼
岂不知家语之不足言而引之耶又岂自无所见而
但据家语以为说乎双峰力诋家语之不足信遂分
卷五 第 6b 页 WYG0204-0813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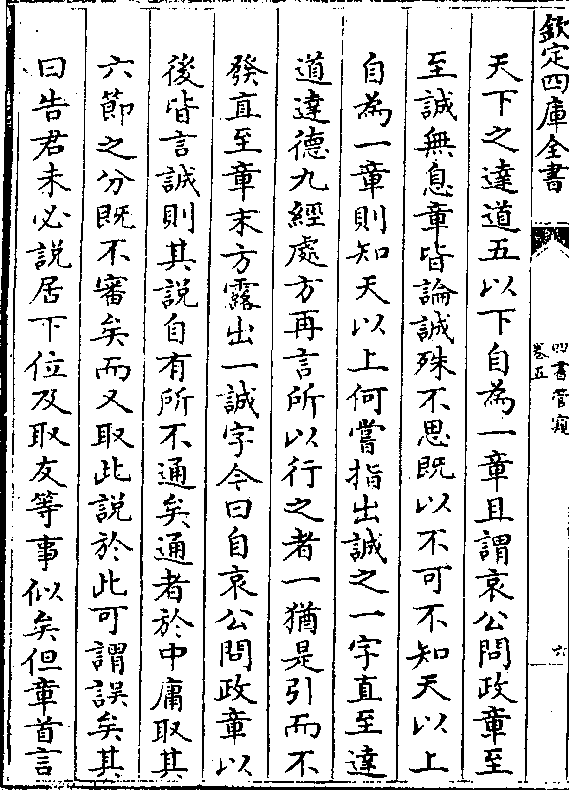 天下之达道五以下自为一章且谓哀公问政章至
天下之达道五以下自为一章且谓哀公问政章至至诚无息章皆论诚殊不思既以不可不知天以上
自为一章则知天以上何尝指出诚之一字直至达
道达德九经处方再言所以行之者一犹是引而不
𤼵直至章末方露出一诚字今曰自哀公问政章以
后皆言诚则其说自有所不通矣通者于中庸取其
六节之分既不审矣而又取此说于此可谓误矣其
曰告君未必说居下位及取友等事似矣但章首言
卷五 第 7a 页 WYG0204-0813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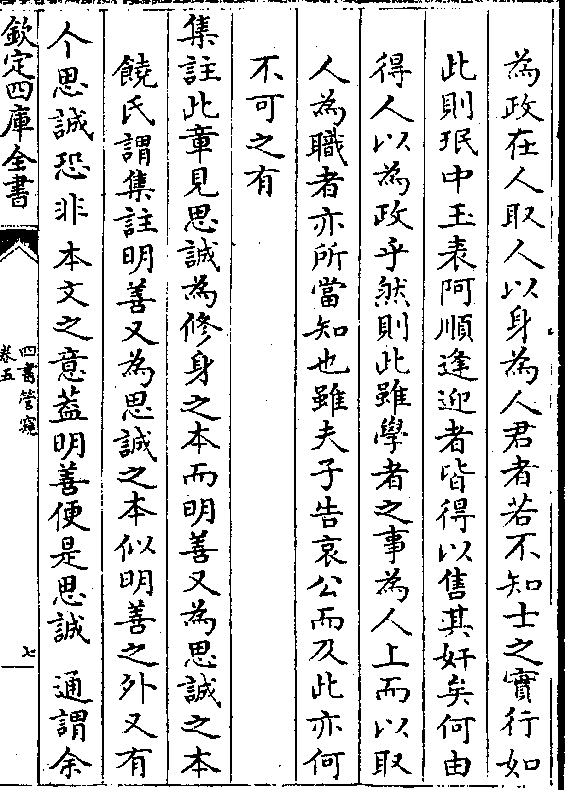 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为人君者若不知士之实行如
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为人君者若不知士之实行如此则珉中玉表阿顺逢迎者皆得以售其奸矣何由
得人以为政乎然则此虽学者之事为人上而以取
人为职者亦所当知也虽夫子告哀公而及此亦何
不可之有
集注此章见思诚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为思诚之本
饶氏谓集注明善又为思诚之本似明善之外又有
个思诚恐非本文之意盖明善便是思诚 通谓余
卷五 第 7b 页 WYG0204-0813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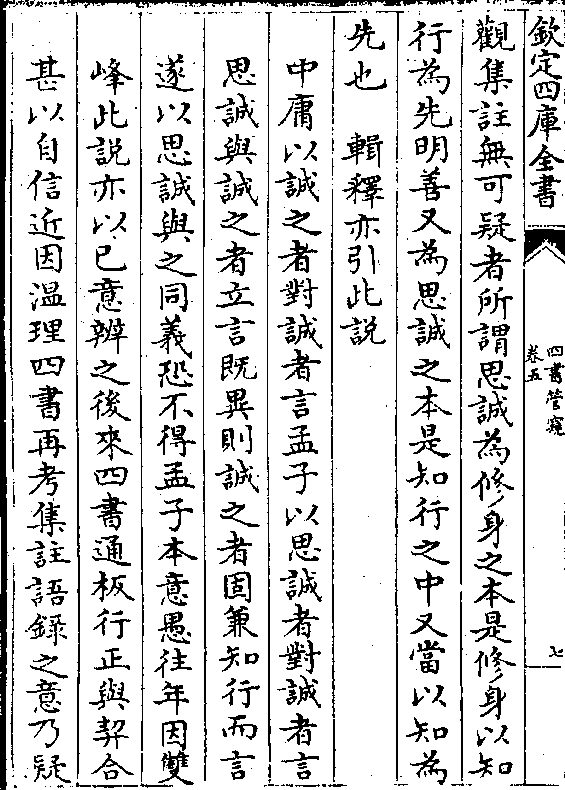 观集注无可疑者所谓思诚为修身之本是修身以知
观集注无可疑者所谓思诚为修身之本是修身以知行为先明善又为思诚之本是知行之中又当以知为
先也 辑释亦引此说
中庸以诚之者对诚者言孟子以思诚者对诚者言
思诚与诚之者立言既异则诚之者固兼知行而言
遂以思诚与之同义恐不得孟子本意愚往年因双
峰此说亦以己意辨之后来四书通板行正与契合
甚以自信近因温理四书再考集注语录之意乃疑
卷五 第 8a 页 WYG0204-0814a.png
 前辩之未当岂双峰所疑却是孟子朱子本意耶谨
前辩之未当岂双峰所疑却是孟子朱子本意耶谨按语录有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诚自是思诚明善是
格物致知思诚是毋自欺谨独明善固所以思诚而
思诚上面更有工夫在此言正是荅学者思诚莫须
明善否之问似与集注语脉相类又按论语九思章
集注引谢氏之言曰未至于从容中道无时而不自
省察也虽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谓思诚此意又与
语录思诚是毋自欺谨独之言相合岂朱子直以思
卷五 第 8b 页 WYG0204-0814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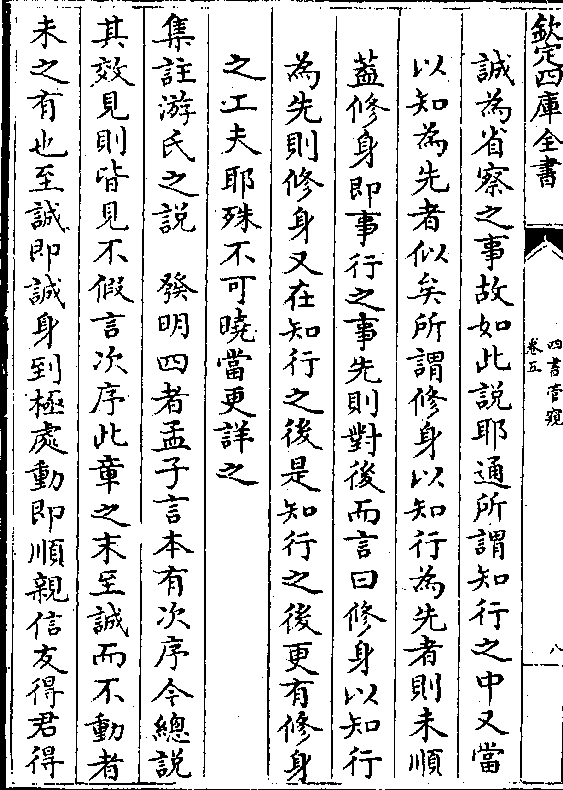 诚为省察之事故如此说耶通所谓知行之中又当
诚为省察之事故如此说耶通所谓知行之中又当以知为先者似矣所谓修身以知行为先者则未顺
盖修身即事行之事先则对后而言曰修身以知行
为先则修身又在知行之后是知行之后更有修身
之工夫耶殊不可晓当更详之
集注游氏之说 𤼵明四者孟子言本有次序今总说
其效见则皆见不假言次序此章之末至诚而不动者
未之有也至诚即诚身到极处动即顺亲信友得君得
卷五 第 9a 页 WYG0204-0814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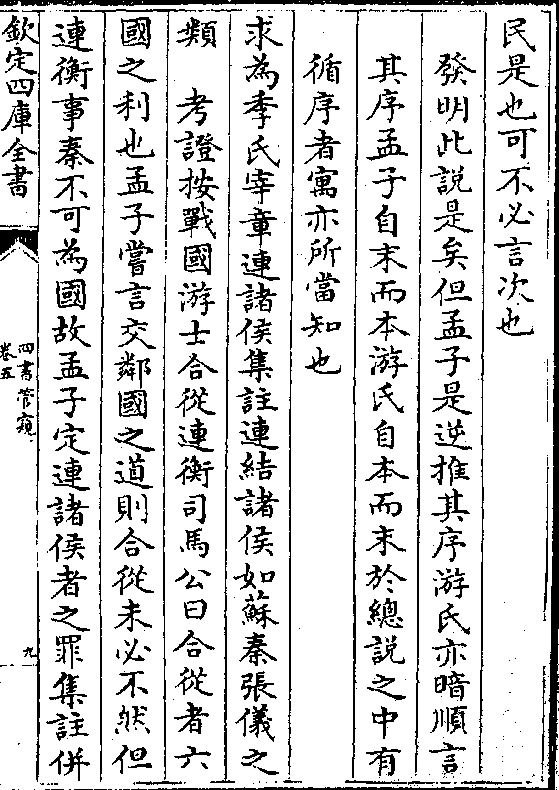 民是也可不必言次也
民是也可不必言次也𤼵明此说是矣但孟子是逆推其序游氏亦暗顺言
其序孟子自末而本游氏自本而末于总说之中有
循序者寓亦所当知也
求为季氏宰章连诸侯集注连结诸侯如苏秦张仪之
类 考證按战国游士合从连衡司马公曰合从者六
国之利也孟子尝言交邻国之道则合从未必不然但
连衡事秦不可为国故孟子定连诸侯者之罪集注并
卷五 第 9b 页 WYG0204-0814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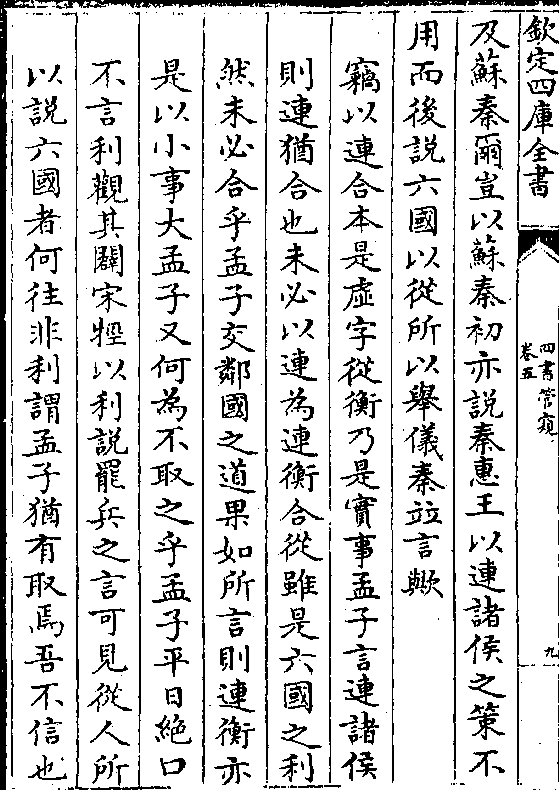 及苏秦尔岂以苏秦初亦说秦惠王以连诸侯之策不
及苏秦尔岂以苏秦初亦说秦惠王以连诸侯之策不用而后说六国以从所以举仪秦并言欤
窃以连合本是虚字从衡乃是实事孟子言连诸侯
则连犹合也未必以连为连衡合从虽是六国之利
然未必合乎孟子交邻国之道果如所言则连衡亦
是以小事大孟子又何为不取之乎孟子平日绝口
不言利观其辟宋牼以利说罢兵之言可见从人所
以说六国者何往非利谓孟子犹有取焉吾不信也
卷五 第 10a 页 WYG0204-0815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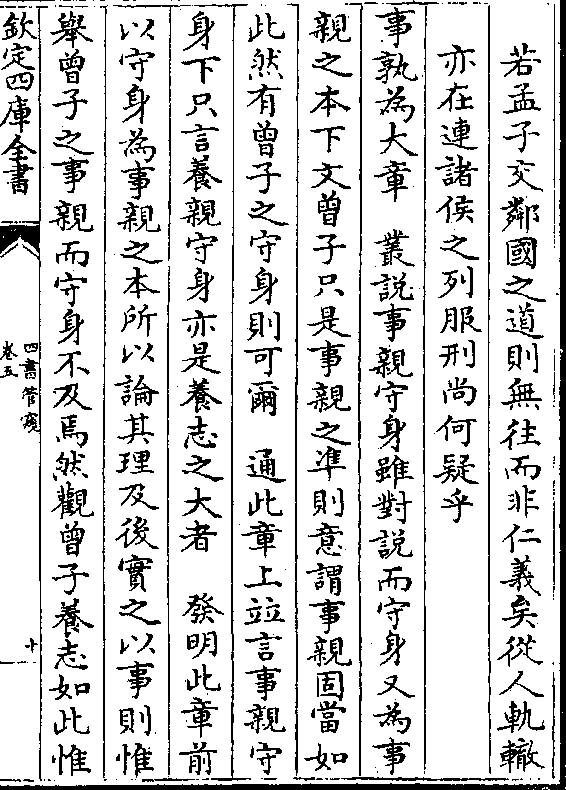 若孟子交邻国之道则无往而非仁义矣从人轨辙
若孟子交邻国之道则无往而非仁义矣从人轨辙亦在连诸侯之列服刑尚何疑乎
事孰为大章 丛说事亲守身虽对说而守身又为事
亲之本下文曾子只是事亲之准则意谓事亲固当如
此然有曾子之守身则可尔 通此章上并言事亲守
身下只言养亲守身亦是养志之大者 𤼵明此章前
以守身为事亲之本所以论其理及后实之以事则惟
举曾子之事亲而守身不及焉然观曾子养志如此惟
卷五 第 10b 页 WYG0204-0815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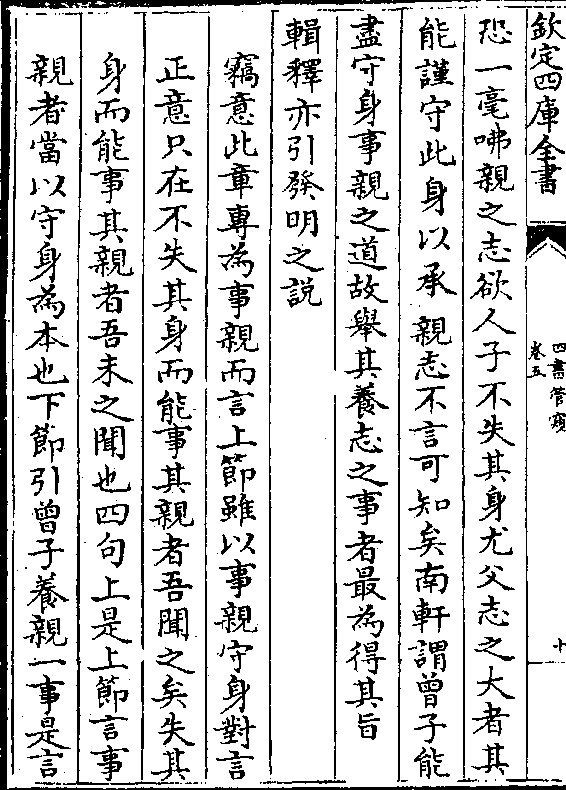 恐一毫咈亲之志欲人子不失其身尤父志之大者其
恐一毫咈亲之志欲人子不失其身尤父志之大者其能谨守此身以承亲志不言可知矣南轩谓曾子能
尽守身事亲之道故举其养志之事者最为得其旨
辑释亦引𤼵明之说
窃意此章专为事亲而言上节虽以事亲守身对言
正意只在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
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四句上是上节言事
亲者当以守身为本也下节引曾子养亲一事是言
卷五 第 11a 页 WYG0204-0815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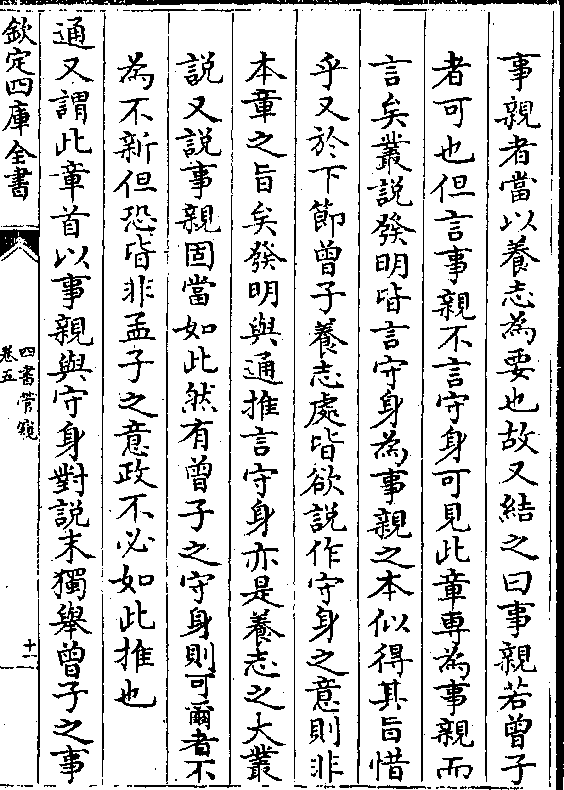 事亲者当以养志为要也故又结之曰事亲若曾子
事亲者当以养志为要也故又结之曰事亲若曾子者可也但言事亲不言守身可见此章专为事亲而
言矣丛说𤼵明皆言守身为事亲之本似得其旨惜
乎又于下节曾子养志处皆欲说作守身之意则非
本章之旨矣𤼵明与通推言守身亦是养志之大丛
说又说事亲固当如此然有曾子之守身则可尔者不
为不新但恐皆非孟子之意政不必如此推也
通又谓此章首以事亲与守身对说末独举曾子之事
卷五 第 11b 页 WYG0204-0815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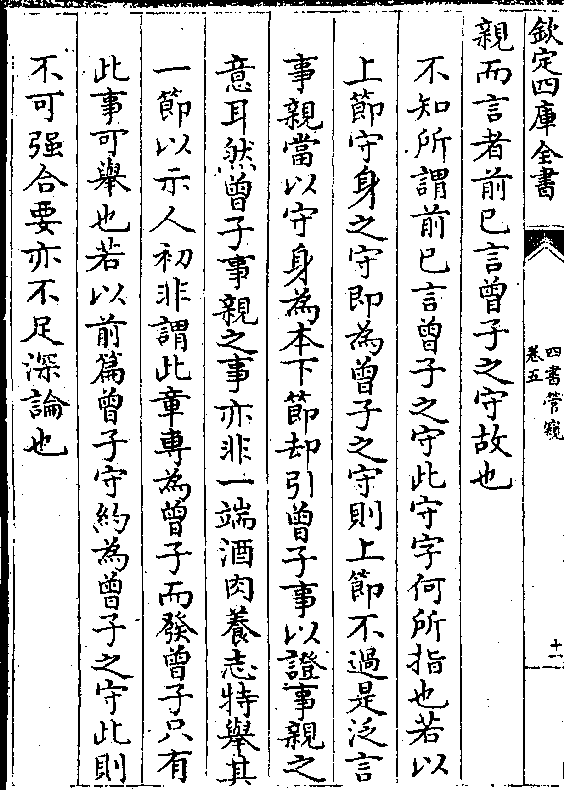 亲而言者前已言曾子之守故也
亲而言者前已言曾子之守故也不知所谓前已言曾子之守此守字何所指也若以
上节守身之守即为曾子之守则上节不过是泛言
事亲当以守身为本下节却引曾子事以證事亲之
意耳然曾子事亲之事亦非一端酒肉养志特举其
一节以示人初非谓此章专为曾子而𤼵曾子只有
此事可举也若以前篇曾子守约为曾子之守此则
不可强合要亦不足深论也
卷五 第 12a 页 WYG0204-0816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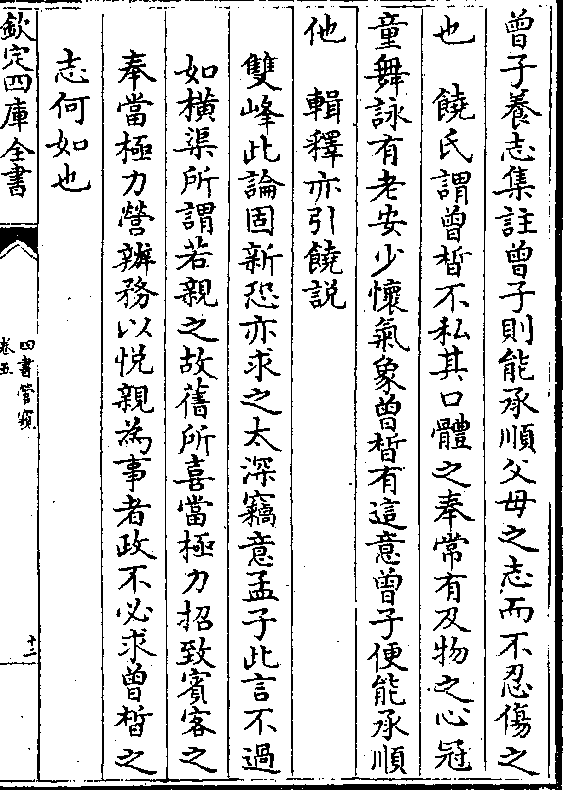 曾子养志集注曾子则能承顺父母之志而不忍伤之
曾子养志集注曾子则能承顺父母之志而不忍伤之也 饶氏谓曾晰不私其口体之奉常有及物之心冠
童舞咏有老安少怀气象曾晰有这意曾子便能承顺
他 辑释亦引饶说
双峰此论固新恐亦求之太深窃意孟子此言不过
如横渠所谓若亲之故旧所喜当极力招致宾客之
奉当极力营办务以悦亲为事者政不必求曾晰之
志何如也
卷五 第 12b 页 WYG0204-0816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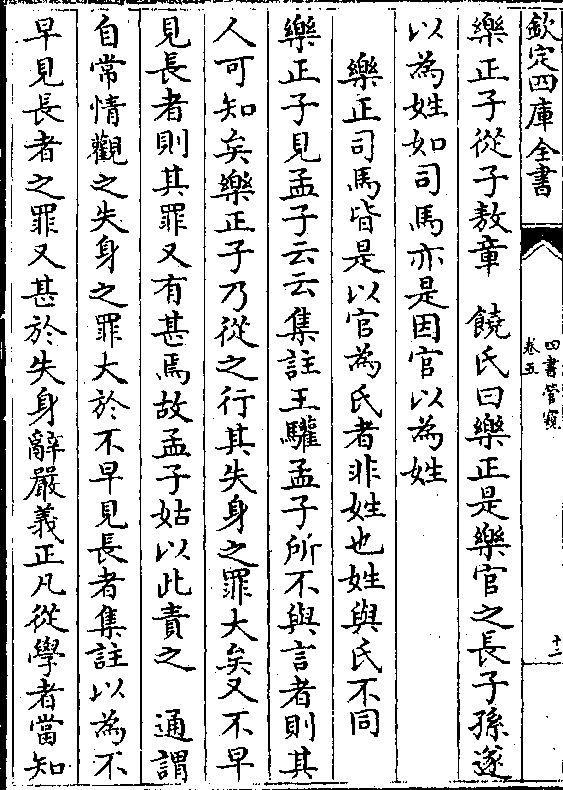 乐正子从子敖章 饶氏曰乐正是乐官之长子孙遂
乐正子从子敖章 饶氏曰乐正是乐官之长子孙遂以为姓如司马亦是因官以为姓
乐正司马皆是以官为氏者非姓也姓与氏不同
乐正子见孟子云云集注王驩孟子所不与言者则其
人可知矣乐正子乃从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
见长者则其罪又有甚焉故孟子姑以此责之 通谓
自常情观之失身之罪大于不早见长者集注以为不
早见长者之罪又甚于失身辞严义正凡从学者当知
卷五 第 13a 页 WYG0204-0816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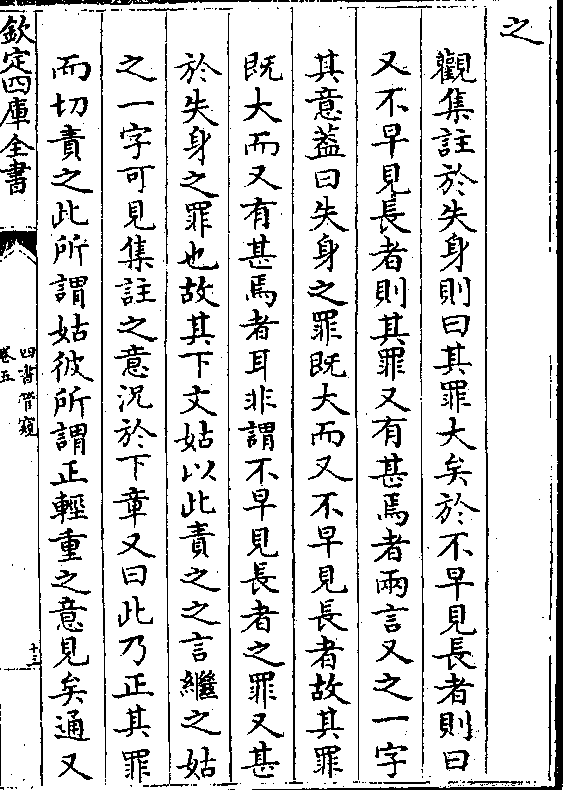 之
之观集注于失身则曰其罪大矣于不早见长者则曰
又不早见长者则其罪又有甚焉者两言又之一字
其意盖曰失身之罪既大而又不早见长者故其罪
既大而又有甚焉者耳非谓不早见长者之罪又甚
于失身之罪也故其下文姑以此责之之言继之姑
之一字可见集注之意况于下章又曰此乃正其罪
而切责之此所谓姑彼所谓正轻重之意见矣通又
卷五 第 13b 页 WYG0204-0816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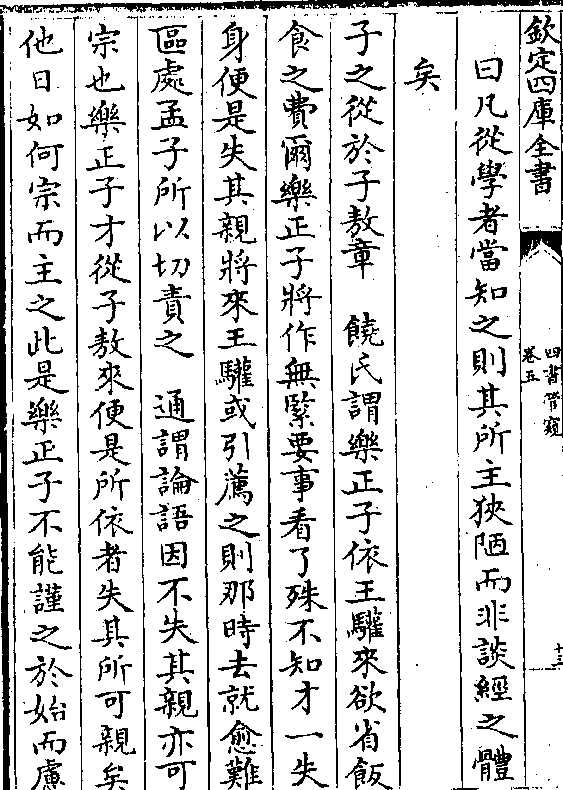 曰凡从学者当知之则其所主狭陋而非谈经之体
曰凡从学者当知之则其所主狭陋而非谈经之体矣
子之从于子敖章 饶氏谓乐正子依王驩来欲省饭
食之费尔乐正子将作无𦂳要事看了殊不知才一失
身便是失其亲将来王驩或引荐之则那时去就愈难
区处孟子所以切责之 通谓论语因不失其亲亦可
宗也乐正子才从子敖来便是所依者失其所可亲矣
他日如何宗而主之此是乐正子不能谨之于始而虑
卷五 第 14a 页 WYG0204-0817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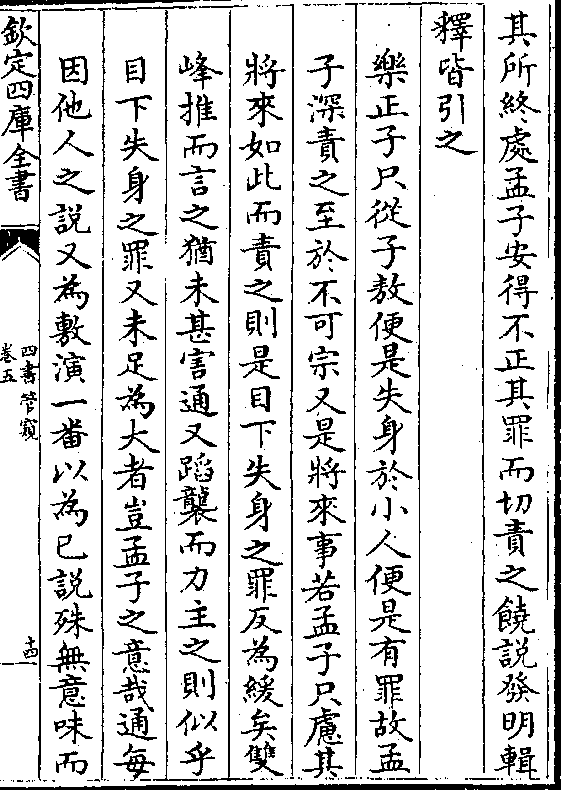 其所终处孟子安得不正其罪而切责之饶说𤼵明辑
其所终处孟子安得不正其罪而切责之饶说𤼵明辑释皆引之
乐正子只从子敖便是失身于小人便是有罪故孟
子深责之至于不可宗又是将来事若孟子只虑其
将来如此而责之则是目下失身之罪反为缓矣双
峰推而言之犹未甚害通又蹈袭而力主之则似乎
目下失身之罪又未足为大者岂孟子之意哉通每
因他人之说又为敷演一番以为己说殊无意味而
卷五 第 14b 页 WYG0204-0817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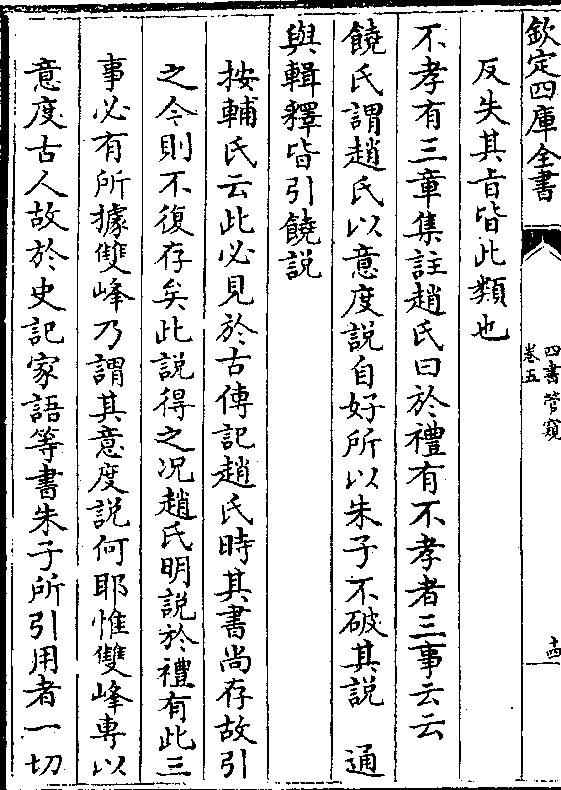 反失其旨皆此类也
反失其旨皆此类也不孝有三章集注赵氏曰于礼有不孝者三事云云
饶氏谓赵氏以意度说自好所以朱子不破其说 通
与辑释皆引饶说
按辅氏云此必见于古传记赵氏时其书尚存故引
之今则不复存矣此说得之况赵氏明说于礼有此三
事必有所据双峰乃谓其意度说何耶惟双峰专以
意度古人故于史记家语等书朱子所引用者一切
卷五 第 15a 页 WYG0204-0817c.png
 皆以意度而不之信噫古书尚不足信双峰又足
皆以意度而不之信噫古书尚不足信双峰又足信乎通既引辅说又引饶说可谓主见不定𤼵明则
专取辅说善矣辑释乃从通而不从𤼵明何耶
仁之实事亲章集注有子以孝悌为为仁之本其意亦
犹此 语录问有子以孝悌为行仁之本孟子以事亲
从兄为仁义之实何也盖孔门论仁举体以该用即所
谓专言之者也孟子言仁必以义配所谓偏言之者也
集疏蔡说与语录同
卷五 第 15b 页 WYG0204-0817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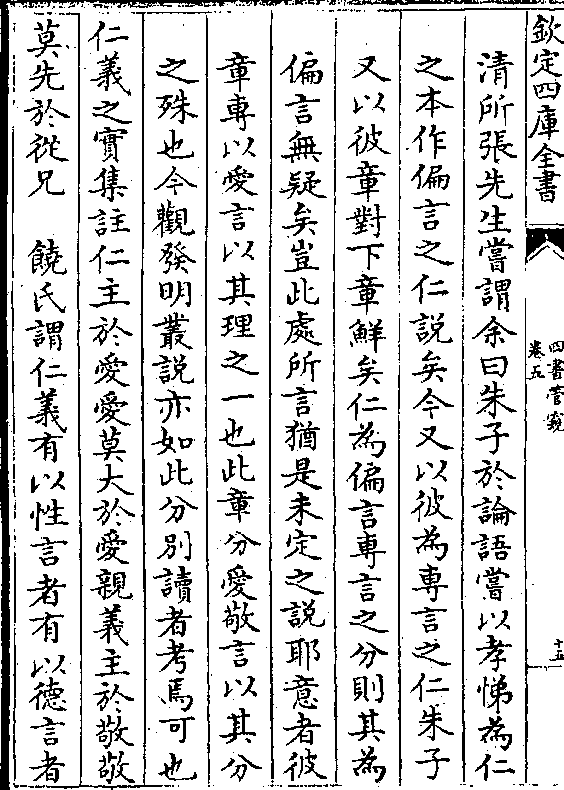 清所张先生尝谓余曰朱子于论语尝以孝悌为仁
清所张先生尝谓余曰朱子于论语尝以孝悌为仁之本作偏言之仁说矣今又以彼为专言之仁朱子
又以彼章对下章鲜矣仁为偏言专言之分则其为
偏言无疑矣岂此处所言犹是未定之说耶意者彼
章专以爱言以其理之一也此章分爱敬言以其分
之殊也今观𤼵明丛说亦如此分别读者考焉可也
仁义之实集注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义主于敬敬
莫先于从兄 饶氏谓仁义有以性言者有以德言者
卷五 第 16a 页 WYG0204-0818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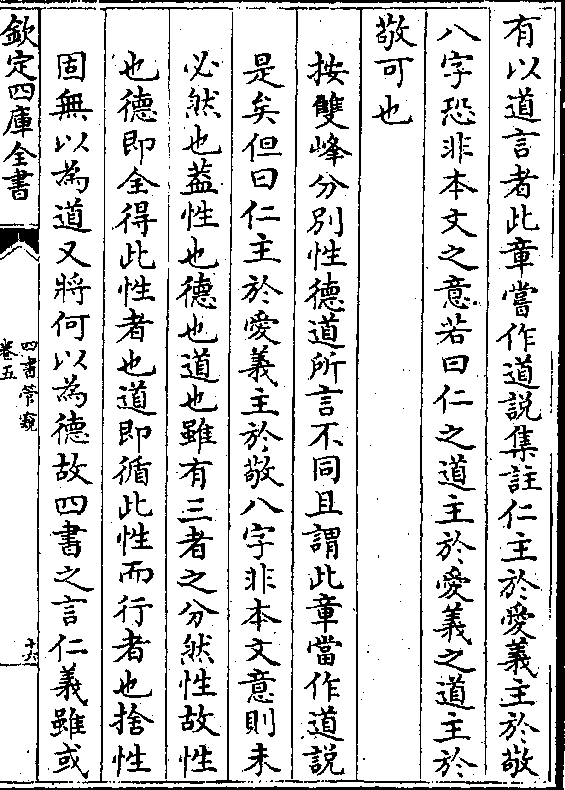 有以道言者此章尝作道说集注仁主于爱义主于敬
有以道言者此章尝作道说集注仁主于爱义主于敬八字恐非本文之意若曰仁之道主于爱义之道主于
敬可也
按双峰分别性德道所言不同且谓此章当作道说
是矣但曰仁主于爱义主于敬八字非本文意则未
必然也盖性也德也道也虽有三者之分然性故性
也德即全得此性者也道即循此性而行者也舍性
固无以为道又将何以为德故四书之言仁义虽或
卷五 第 16b 页 WYG0204-0818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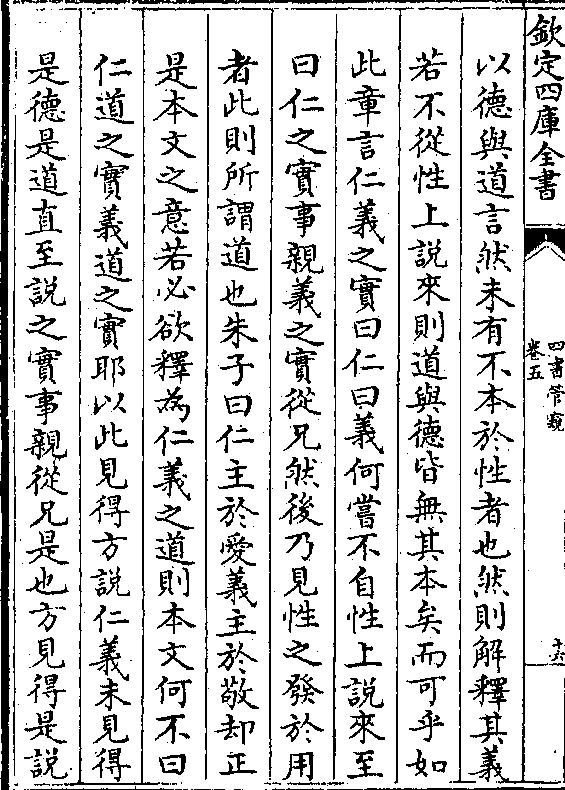 以德与道言然未有不本于性者也然则解释其义
以德与道言然未有不本于性者也然则解释其义若不从性上说来则道与德皆无其本矣而可乎如
此章言仁义之实曰仁曰义何尝不自性上说来至
曰仁之实事亲义之实从兄然后乃见性之𤼵于用
者此则所谓道也朱子曰仁主于爱义主于敬却正
是本文之意若必欲释为仁义之道则本文何不曰
仁道之实义道之实耶以此见得方说仁义未见得
是德是道直至说之实事亲从兄是也方见得是说
卷五 第 17a 页 WYG0204-0818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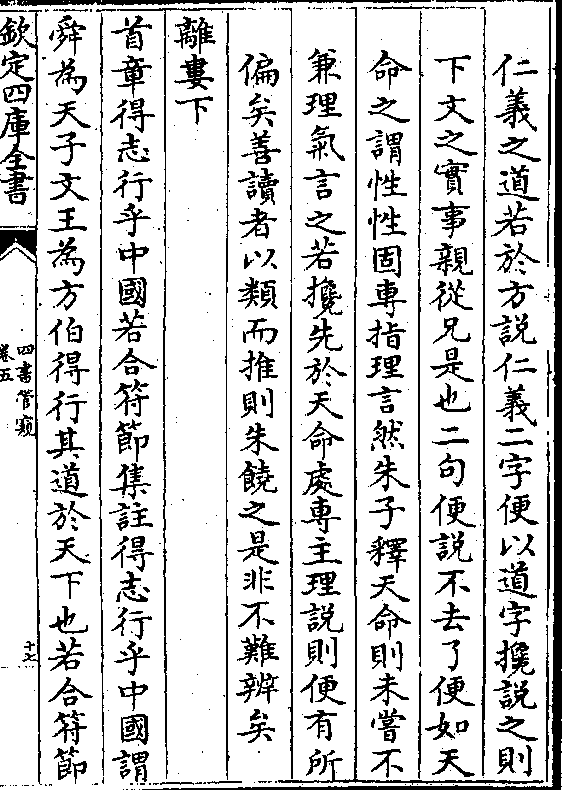 仁义之道若于方说仁义二字便以道字搀说之则
仁义之道若于方说仁义二字便以道字搀说之则下文之实事亲从兄是也二句便说不去了便如天
命之谓性性固专指理言然朱子释天命则未尝不
兼理气言之若搀先于天命处专主理说则便有所
偏矣善读者以类而推则朱饶之是非不难辨矣
离娄下
首章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集注得志行乎中国谓
舜为天子文王为方伯得行其道于天下也若合符节
卷五 第 17b 页 WYG0204-0818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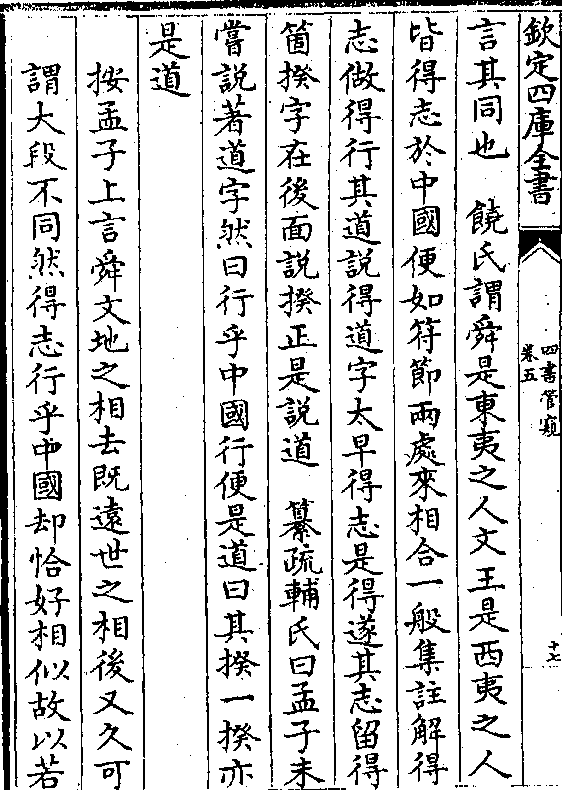 言其同也 饶氏谓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
言其同也 饶氏谓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皆得志于中国便如符节两处来相合一般集注解得
志做得行其道说得道字太早得志是得遂其志留得
个揆字在后面说揆正是说道 纂疏辅氏曰孟子末
尝说著道字然曰行乎中国行便是道曰其揆一揆亦
是道
按孟子上言舜文地之相去既远世之相后又久可
谓大段不同然得志行乎中国却恰好相似故以若
卷五 第 18a 页 WYG0204-0819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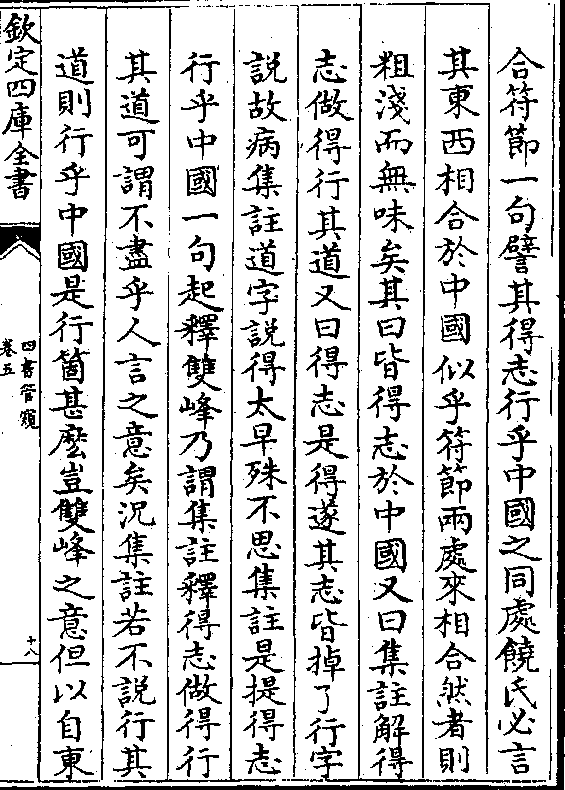 合符节一句譬其得志行乎中国之同处饶氏必言
合符节一句譬其得志行乎中国之同处饶氏必言其东西相合于中国似乎符节两处来相合然者则
粗浅而无味矣其曰皆得志于中国又曰集注解得
志做得行其道又曰得志是得遂其志皆掉了行字
说故病集注道字说得太早殊不思集注是提得志
行乎中国一句起释双峰乃谓集注释得志做得行
其道可谓不尽乎人言之意矣况集注若不说行其
道则行乎中国是行个甚么岂双峰之意但以自东
卷五 第 18b 页 WYG0204-0819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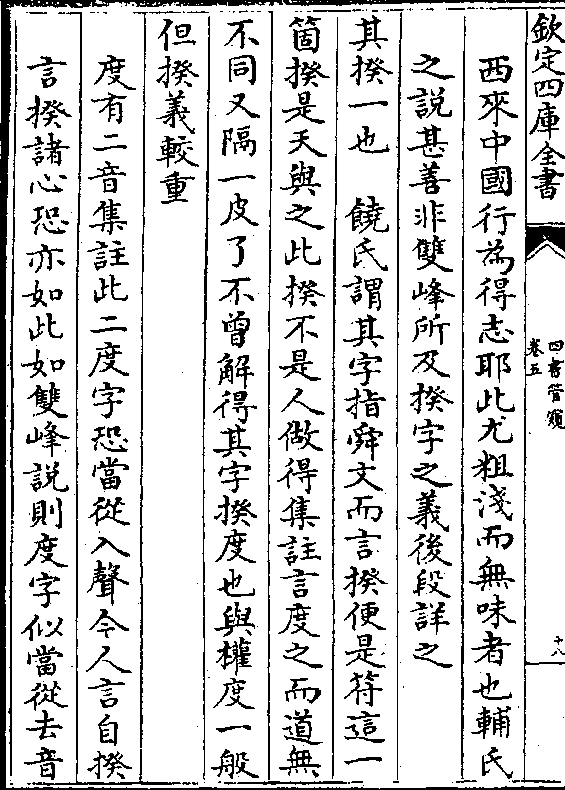 西来中国行为得志耶此尤粗浅而无味者也辅氏
西来中国行为得志耶此尤粗浅而无味者也辅氏之说甚善非双峰所及揆字之义后段详之
其揆一也 饶氏谓其字指舜文而言揆便是符这一
个揆是天与之此揆不是人做得集注言度之而道无
不同又隔一皮了不曾解得其字揆度也与权度一般
但揆义较重
度有二音集注此二度字恐当从入声今人言自揆
言揆诸心恐亦如此如双峰说则度字似当从去音
卷五 第 19a 页 WYG0204-0819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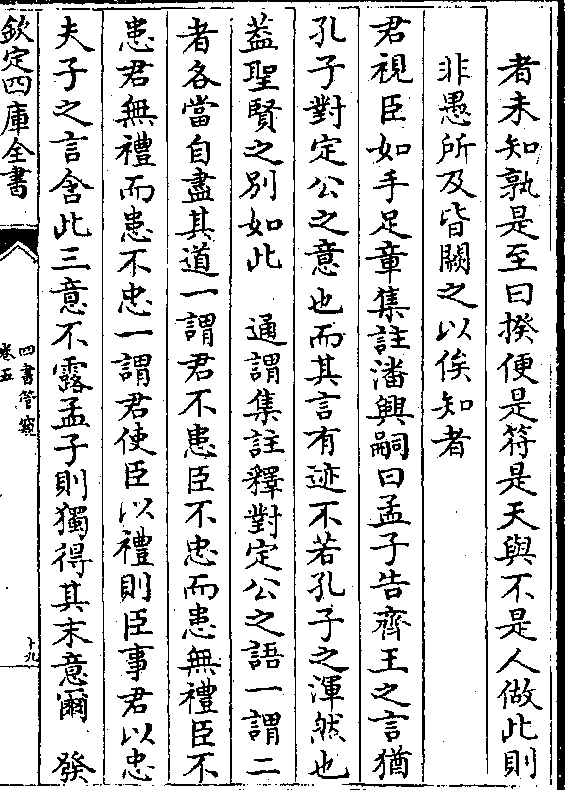 者未知孰是至曰揆便是符是天与不是人做此则
者未知孰是至曰揆便是符是天与不是人做此则非愚所及皆阙之以俟知者
君视臣如手足章集注潘兴嗣曰孟子告齐王之言犹
孔子对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浑然也
盖圣贤之别如此 通谓集注释对定公之语一谓二
者各当自尽其道一谓君不患臣不忠而患无礼臣不
患君无礼而患不忠一谓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
夫子之言含此三意不露孟子则独得其末意尔 𤼵
卷五 第 19b 页 WYG0204-0819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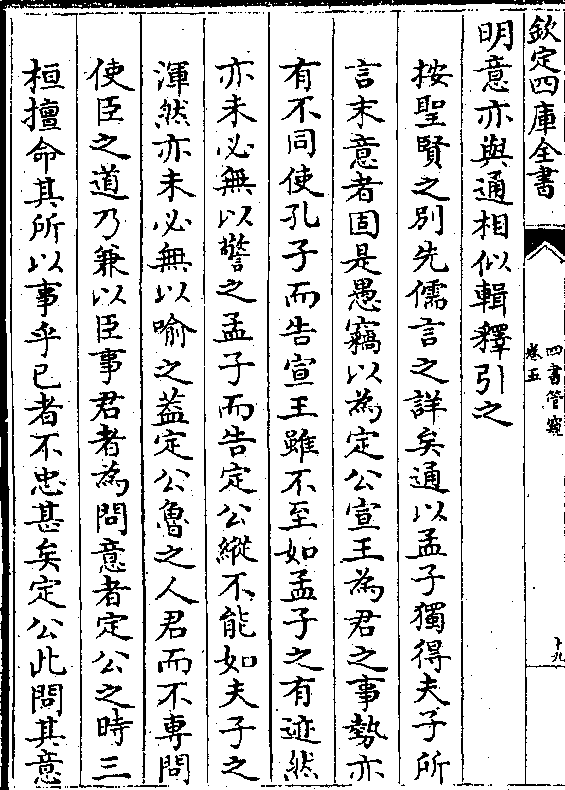 明意亦与通相似辑释引之
明意亦与通相似辑释引之按圣贤之别先儒言之详矣通以孟子独得夫子所
言末意者固是愚窃以为定公宣王为君之事势亦
有不同使孔子而告宣王虽不至如孟子之有迹然
亦未必无以警之孟子而告定公纵不能如夫子之
浑然亦未必无以喻之盖定公鲁之人君而不专问
使臣之道乃兼以臣事君者为问意者定公之时三
桓擅命其所以事乎已者不忠甚矣定公此问其意
卷五 第 20a 页 WYG0204-0820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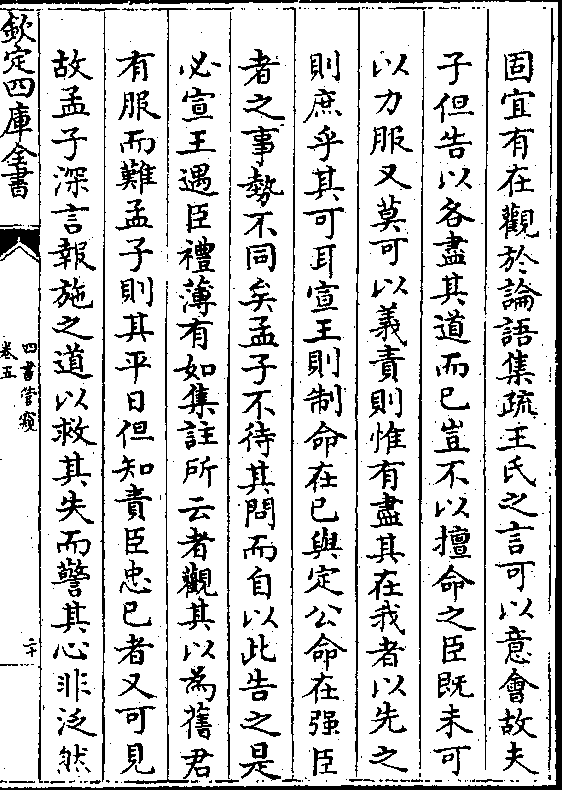 固宜有在观于论语集疏王氏之言可以意会故夫
固宜有在观于论语集疏王氏之言可以意会故夫子但告以各尽其道而已岂不以擅命之臣既未可
以力服又莫可以义责则惟有尽其在我者以先之
则庶乎其可耳宣王则制命在己与定公命在强臣
者之事势不同矣孟子不待其问而自以此告之是
必宣王遇臣礼薄有如集注所云者观其以为旧君
有服而难孟子则其平日但知责臣忠己者又可见
故孟子深言报施之道以救其失而警其心非泛然
卷五 第 20b 页 WYG0204-0820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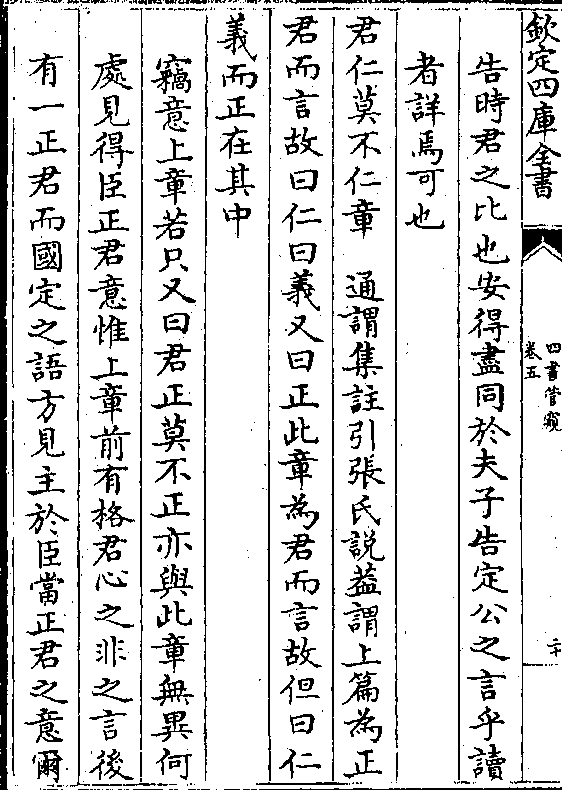 告时君之比也安得尽同于夫子告定公之言乎读
告时君之比也安得尽同于夫子告定公之言乎读者详焉可也
君仁莫不仁章 通谓集注引张氏说盖谓上篇为正
君而言故曰仁曰义又曰正此章为君而言故但曰仁
义而正在其中
窃意上章若只又曰君正莫不正亦与此章无异何
处见得臣正君意惟上章前有格君心之非之言后
有一正君而国定之语方见主于臣当正君之意尔
卷五 第 21a 页 WYG0204-0820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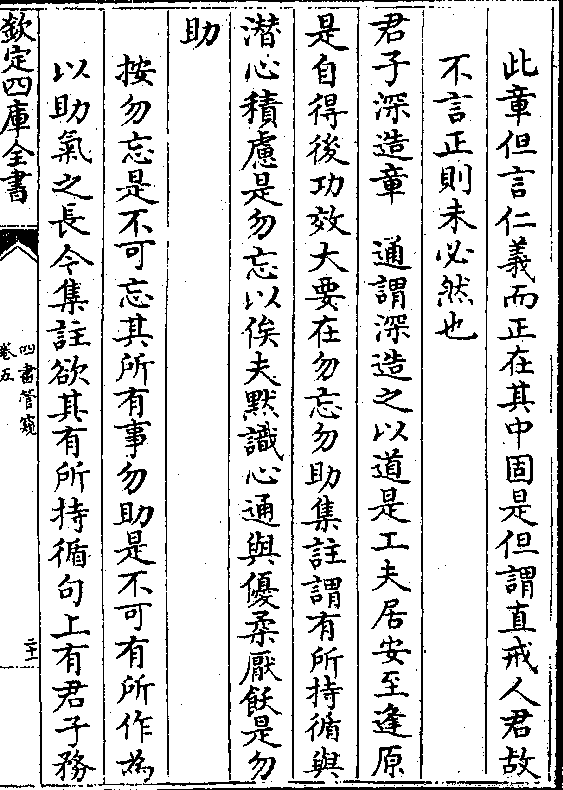 此章但言仁义而正在其中固是但谓直戒人君故
此章但言仁义而正在其中固是但谓直戒人君故不言正则未必然也
君子深造章 通谓深造之以道是工夫居安至逢原
是自得后功效大要在勿忘勿助集注谓有所持循与
潜心积虑是勿忘以俟夫默识心通与优柔厌饫是勿
助
按勿忘是不可忘其所有事勿助是不可有所作为
以助气之长今集注欲其有所持循句上有君子务
卷五 第 21b 页 WYG0204-0820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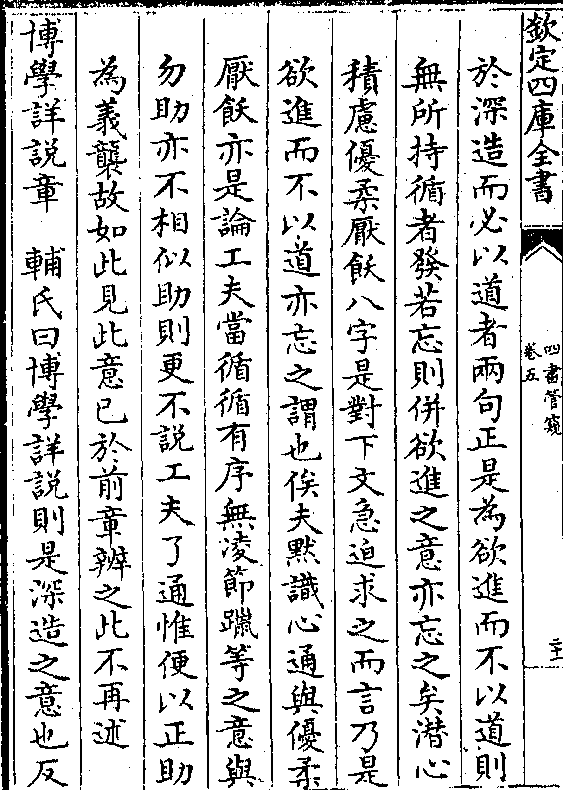 于深造而必以道者两句正是为欲进而不以道则
于深造而必以道者两句正是为欲进而不以道则无所持循者𤼵若忘则并欲进之意亦忘之矣潜心
积虑优柔厌饫八字是对下文急迫求之而言乃是
欲进而不以道亦忘之谓也俟夫默识心通与优柔
厌饫亦是论工夫当循循有序无凌节躐等之意与
勿助亦不相似助则更不说工夫了通惟便以正助
为义袭故如此见此意已于前章辨之此不再述
博学详说章 辅氏曰博学详说则是深造之意也反
卷五 第 22a 页 WYG0204-0821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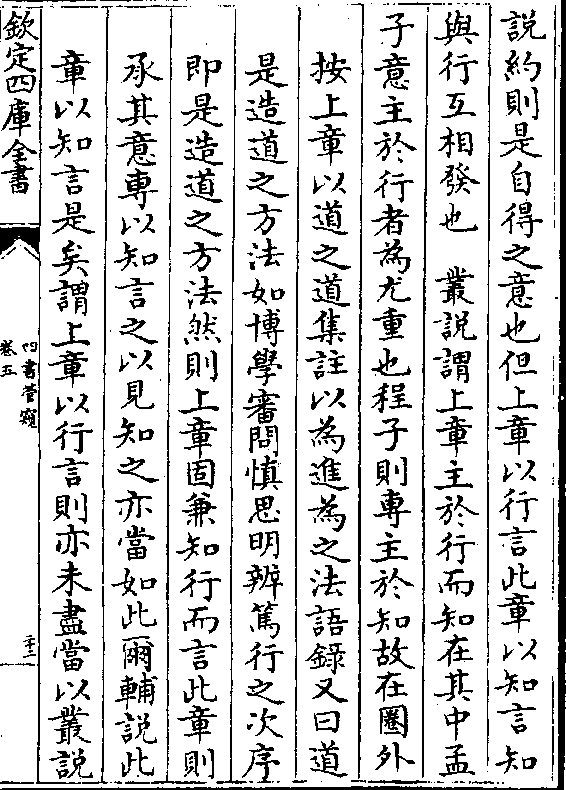 说约则是自得之意也但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知
说约则是自得之意也但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知与行互相𤼵也 丛说谓上章主于行而知在其中孟
子意主于行者为尤重也程子则专主于知故在圈外
按上章以道之道集注以为进为之法语录又曰道
是造道之方法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次序
即是造道之方法然则上章固兼知行而言此章则
承其意专以知言之以见知之亦当如此尔辅说此
章以知言是矣谓上章以行言则亦未尽当以丛说
卷五 第 22b 页 WYG0204-0821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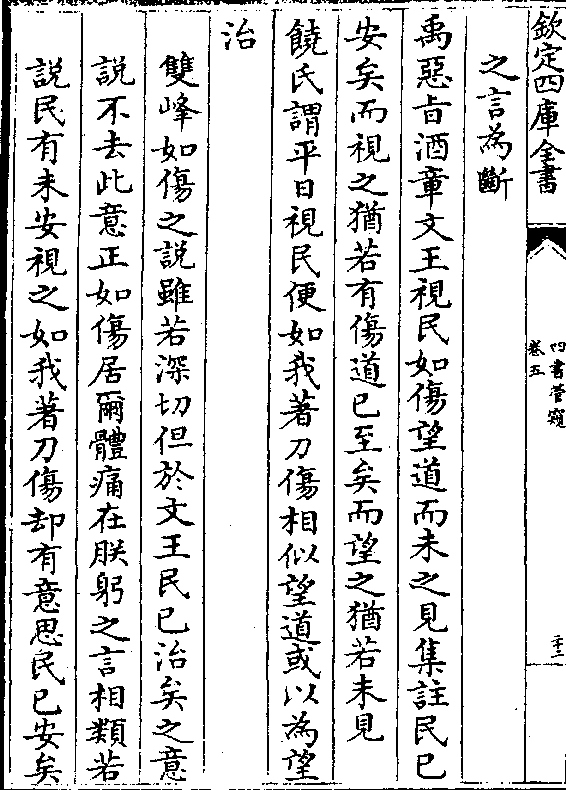 之言为断
之言为断禹恶旨酒章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集注民已
安矣而视之犹若有伤道已至矣而望之犹若未见
饶氏谓平日视民便如我著刀伤相似望道或以为望
治
双峰如伤之说虽若深切但于文王民已治矣之意
说不去此意正如伤居尔体痛在朕躬之言相类若
说民有未安视之如我著刀伤却有意思民已安矣
卷五 第 23a 页 WYG0204-0821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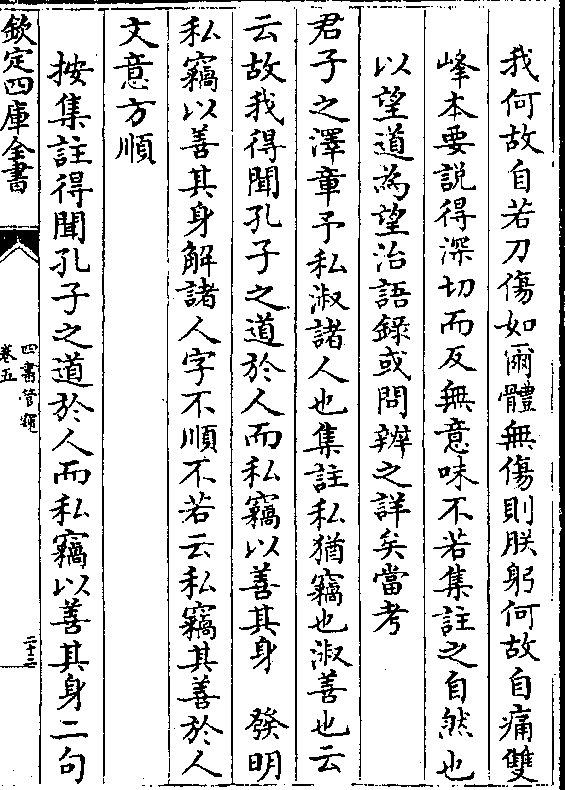 我何故自若刀伤如尔体无伤则朕躬何故自痛双
我何故自若刀伤如尔体无伤则朕躬何故自痛双峰本要说得深切而反无意味不若集注之自然也
以望道为望治语录或问辨之详矣当考
君子之泽章予私淑诸人也集注私犹窃也淑善也云
云故我得闻孔子之道于人而私窃以善其身 𤼵明
私窃以善其身解诸人字不顺不若云私窃其善于人
文意方顺
按集注得闻孔子之道于人而私窃以善其身二句
卷五 第 23b 页 WYG0204-0821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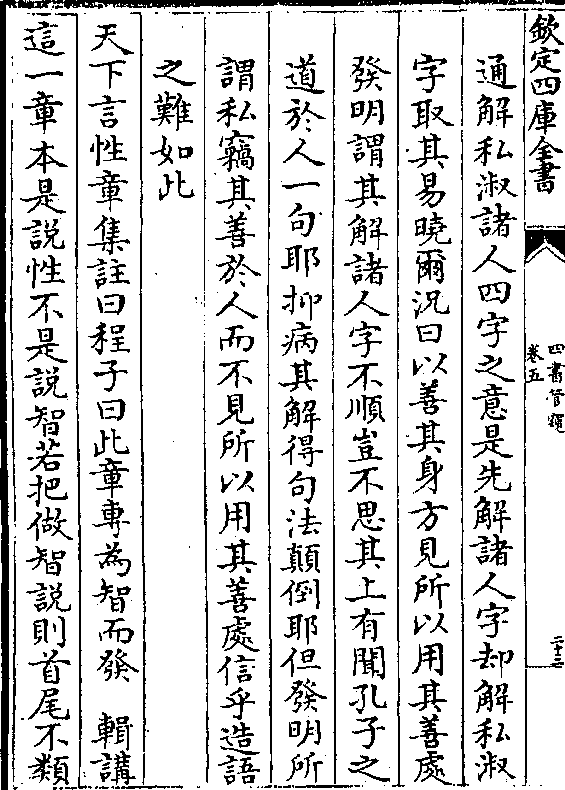 通解私淑诸人四字之意是先解诸人字却解私淑
通解私淑诸人四字之意是先解诸人字却解私淑字取其易晓尔况曰以善其身方见所以用其善处
𤼵明谓其解诸人字不顺岂不思其上有闻孔子之
道于人一句耶抑病其解得句法颠倒耶但𤼵明所
谓私窃其善于人而不见所以用其善处信乎造语
之难如此
天下言性章集注曰程子曰此章专为智而𤼵 辑讲
这一章本是说性不是说智若把做智说则首尾不类
卷五 第 24a 页 WYG0204-0822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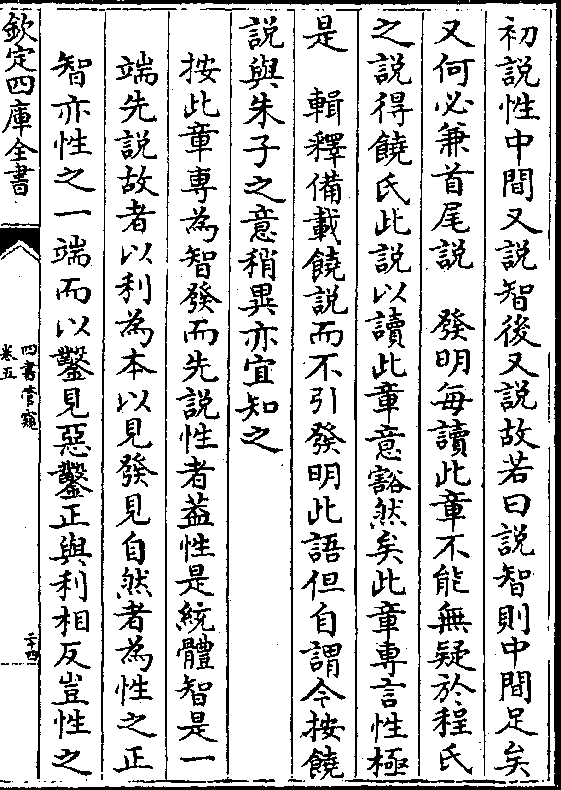 初说性中间又说智后又说故若曰说智则中间足矣
初说性中间又说智后又说故若曰说智则中间足矣又何必兼首尾说 𤼵明每读此章不能无疑于程氏
之说得饶氏此说以读此章意豁然矣此章专言性极
是 辑释备载饶说而不引𤼵明此语但自谓今按饶
说与朱子之意稍异亦宜知之
按此章专为智𤼵而先说性者盖性是统体智是一
端先说故者以利为本以见发见自然者为性之正
智亦性之一端而以凿见恶凿正与利相反岂性之
卷五 第 24b 页 WYG0204-0822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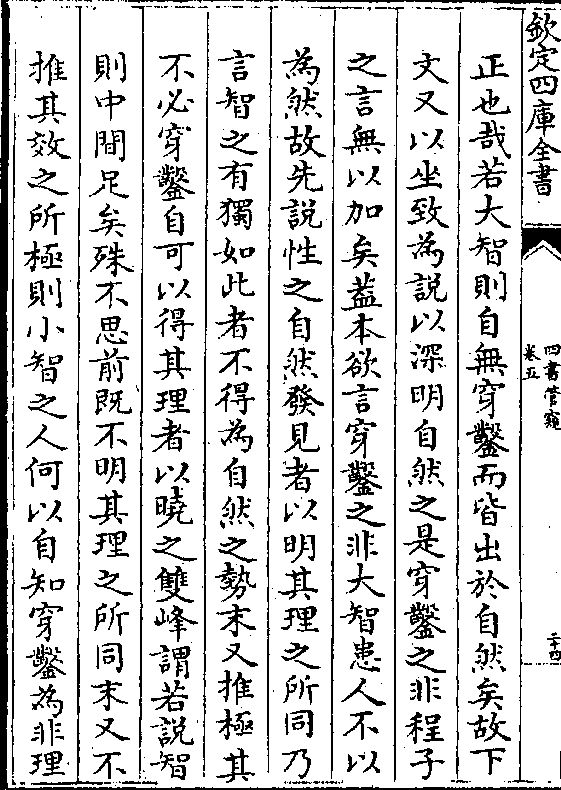 正也哉若大智则自无穿凿而皆出于自然矣故下
正也哉若大智则自无穿凿而皆出于自然矣故下文又以坐致为说以深明自然之是穿凿之非程子
之言无以加矣盖本欲言穿凿之非大智患人不以
为然故先说性之自然𤼵见者以明其理之所同乃
言智之有独如此者不得为自然之势末又推极其
不必穿凿自可以得其理者以晓之双峰谓若说智
则中间足矣殊不思前既不明其理之所同末又不
推其效之所极则小智之人何以自知穿凿为非理
卷五 第 25a 页 WYG0204-0822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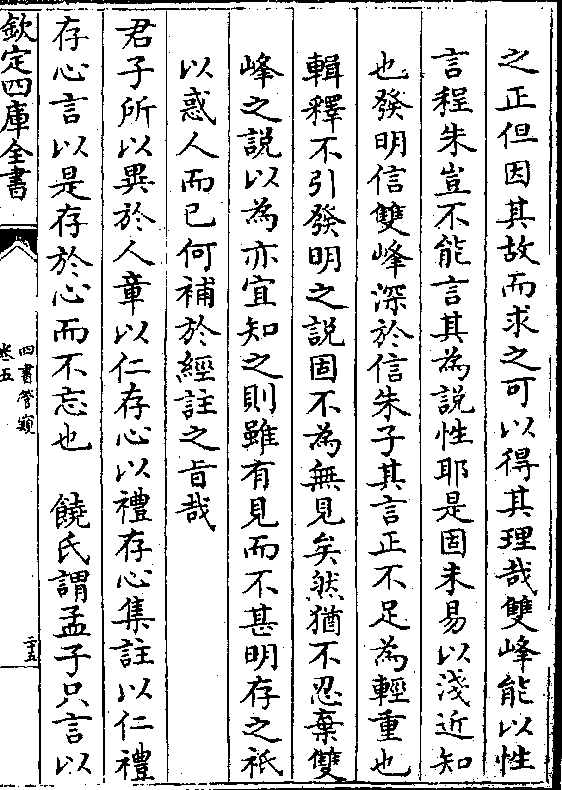 之正但因其故而求之可以得其理哉双峰能以性
之正但因其故而求之可以得其理哉双峰能以性言程朱岂不能言其为说性耶是固未易以浅近知
也𤼵明信双峰深于信朱子其言正不足为轻重也
辑释不引𤼵明之说固不为无见矣然犹不忍弃双
峰之说以为亦宜知之则虽有见而不甚明存之祇
以惑人而已何补于经注之旨哉
君子所以异于人章以仁存心以礼存心集注以仁礼
存心言以是存于心而不忘也 饶氏谓孟子只言以
卷五 第 25b 页 WYG0204-0822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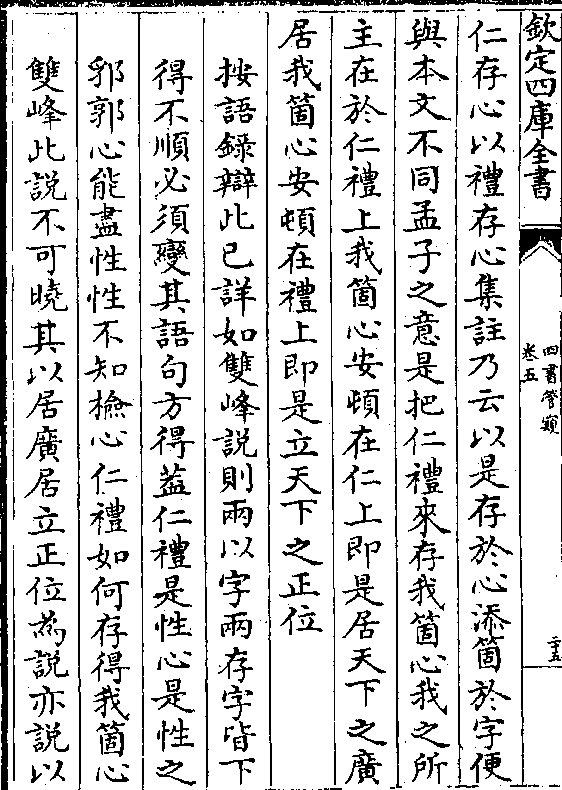 仁存心以礼存心集注乃云以是存于心添个于字便
仁存心以礼存心集注乃云以是存于心添个于字便与本文不同孟子之意是把仁礼来存我个心我之所
主在于仁礼上我个心安顿在仁上即是居天下之广
居我个心安顿在礼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
按语录辩此已详如双峰说则两以字两存字皆下
得不顺必须变其语句方得盖仁礼是性心是性之
郛郭心能尽性性不知检心仁礼如何存得我个心
双峰此说不可晓其以居广居立正位为说亦说以
卷五 第 26a 页 WYG0204-0823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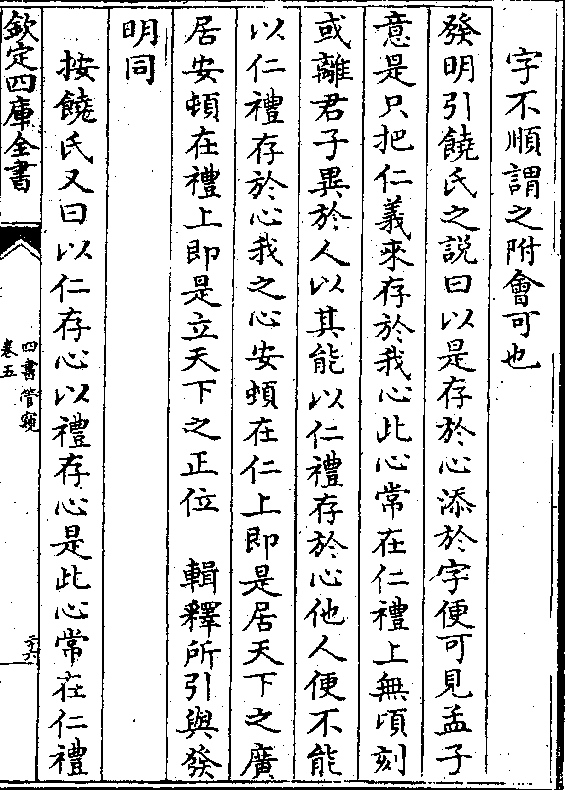 字不顺谓之附会可也
字不顺谓之附会可也𤼵明引饶氏之说曰以是存于心添于字便可见孟子
意是只把仁义来存于我心此心常在仁礼上无顷刻
或离君子异于人以其能以仁礼存于心他人便不能
以仁礼存于心我之心安顿在仁上即是居天下之广
居安顿在礼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 辑释所引与𤼵
明同
按饶氏又曰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是此心常在仁礼
卷五 第 26b 页 WYG0204-0823b.png
 上无顷刻之或离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
上无顷刻之或离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耳他人便不能以仁礼存心饶氏此一段说与前段
说本皆是破集注不合添个于字之意非有所𤼵明
于集注也𤼵明乃合其二段而一之又删润之以求
合于集注之旨似矣但曰此心常在仁礼上与居广
居立正位之證则又只是把心存在仁礼上与集注
正背不可强合譬之二人在此心不相得乃强使之
面目相向若相得者不知其情意气色终不可掩竟
卷五 第 27a 页 WYG0204-0823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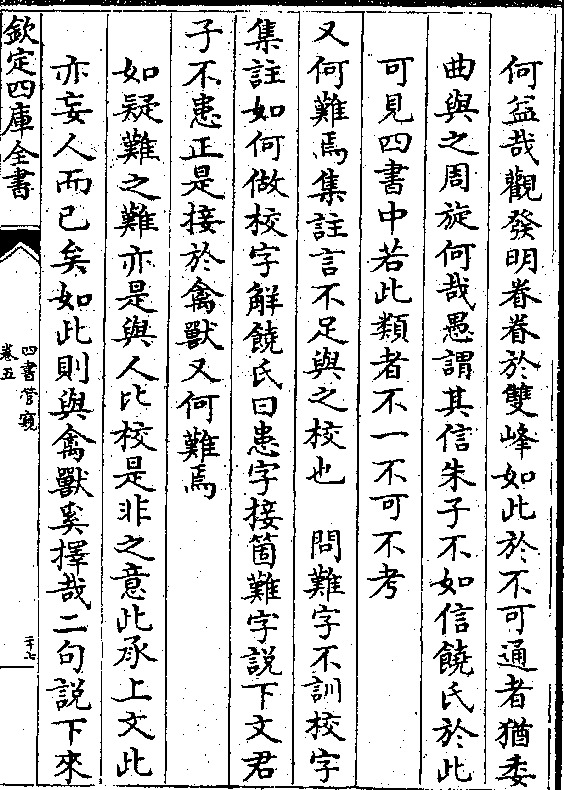 何益哉观𤼵明眷眷于双峰如此于不可通者犹委
何益哉观𤼵明眷眷于双峰如此于不可通者犹委曲与之周旋何哉愚谓其信朱子不如信饶氏于此
可见四书中若此类者不一不可不考
又何难焉集注言不足与之校也 问难字不训校字
集注如何做校字解饶氏曰患字接个难字说下文君
子不患正是接于禽兽又何难焉
如疑难之难亦是与人比校是非之意此承上文此
亦妄人而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二句说下来
卷五 第 27b 页 WYG0204-0823d.png
 则是以其横逆非人所为故不足与之校耳校字虽
则是以其横逆非人所为故不足与之校耳校字虽非难之正训然难亦校之意也盖不校则患无由生
故自无一朝之患不然则妄人所为如禽兽伤人害
物无所忌惮若但以为不足患而不见不校之意则
是己非彼或以为不足患而与之校则小人之锋亦
甚可畏政恐一朝之患有所不免矣古之人如东汉
党锢诸贤与阉寺小人同世至与之校而流毒无穷
皆起于禽兽其人而以为不足患之所见尔然则集
卷五 第 28a 页 WYG0204-0824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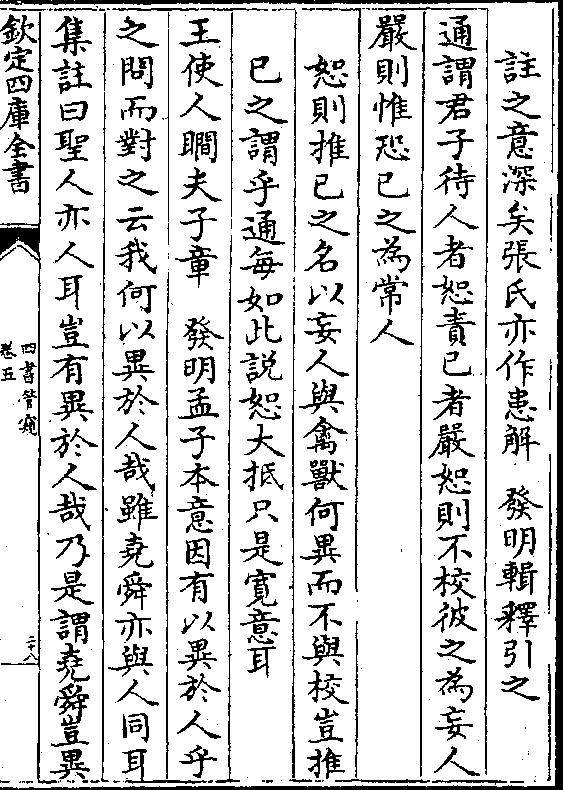 注之意深矣张氏亦作患解 𤼵明辑释引之
注之意深矣张氏亦作患解 𤼵明辑释引之通谓君子待人者恕责己者严恕则不校彼之为妄人
严则惟恐己之为常人
恕则推己之名以妄人与禽兽何异而不与校岂推
己之谓乎通每如此说恕大抵只是宽意耳
王使人瞷夫子章 𤼵明孟子本意因有以异于人乎
之问而对之云我何以异于人哉虽尧舜亦与人同耳
集注曰圣人亦人耳岂有异于人哉乃是谓尧舜岂异
卷五 第 28b 页 WYG0204-0824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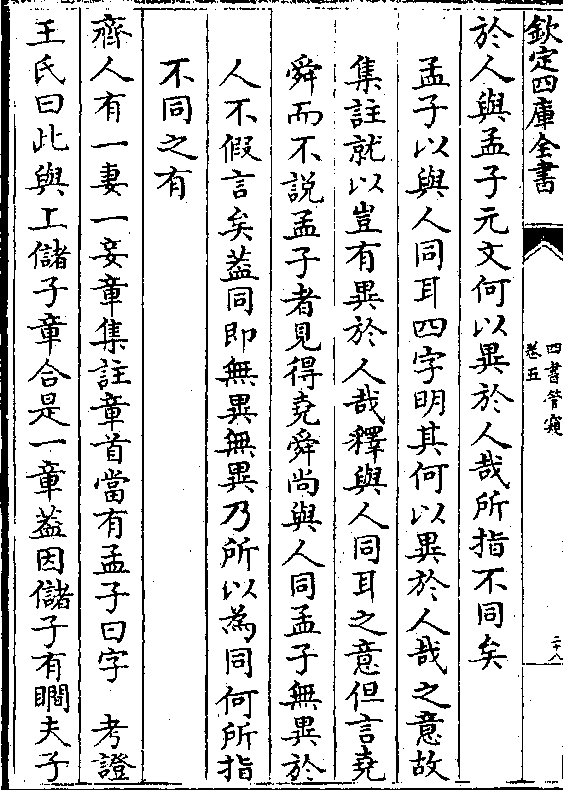 于人与孟子元文何以异于人哉所指不同矣
于人与孟子元文何以异于人哉所指不同矣孟子以与人同耳四字明其何以异于人哉之意故
集注就以岂有异于人哉释与人同耳之意但言尧
舜而不说孟子者见得尧舜尚与人同孟子无异于
人不假言矣盖同即无异无异乃所以为同何所指
不同之有
齐人有一妻一妾章集注章首当有孟子曰字 考證
王氏曰此与上储子章合是一章盖因储子有瞷夫子
卷五 第 29a 页 WYG0204-0824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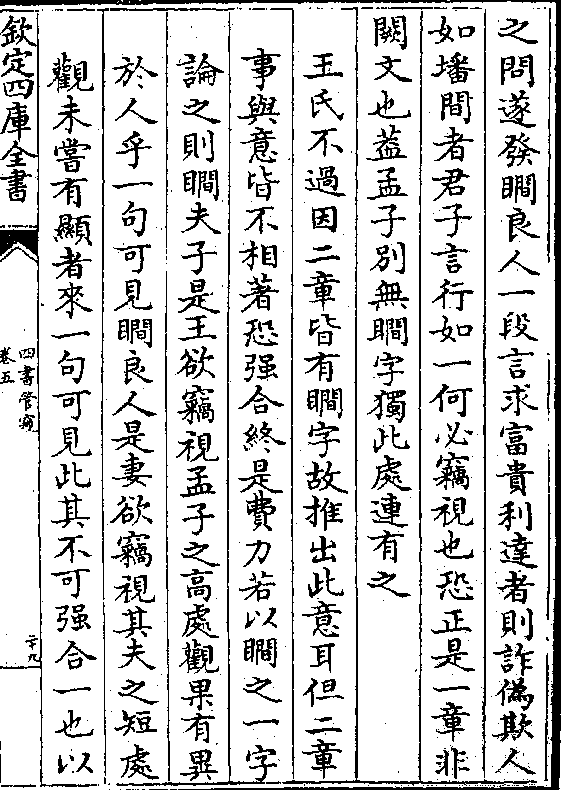 之问遂𤼵瞷良人一段言求富贵利达者则诈伪欺人
之问遂𤼵瞷良人一段言求富贵利达者则诈伪欺人如墦间者君子言行如一何必窃视也恐正是一章非
阙文也盖孟子别无瞷字独此处连有之
王氏不过因二章皆有瞷字故推出此意耳但二章
事与意皆不相著恐强合终是费力若以瞷之一字
论之则瞷夫子是王欲窃视孟子之高处观果有异
于人乎一句可见瞷良人是妻欲窃视其夫之短处
观未尝有显者来一句可见此其不可强合一也以
卷五 第 29b 页 WYG0204-0824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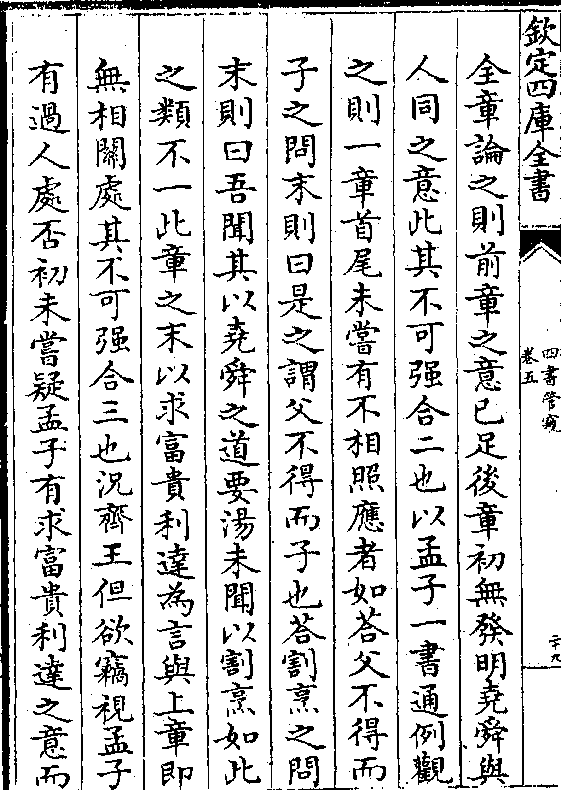 全章论之则前章之意已足后章初无𤼵明尧舜与
全章论之则前章之意已足后章初无𤼵明尧舜与人同之意此其不可强合二也以孟子一书通例观
之则一章首尾未尝有不相照应者如荅父不得而
子之问末则曰是之谓父不得而子也荅割烹之问
末则曰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如此
之类不一此章之末以求富贵利达为言与上章即
无相关处其不可强合三也况齐王但欲窃视孟子
有过人处否初未尝疑孟子有求富贵利达之意而
卷五 第 30a 页 WYG0204-0825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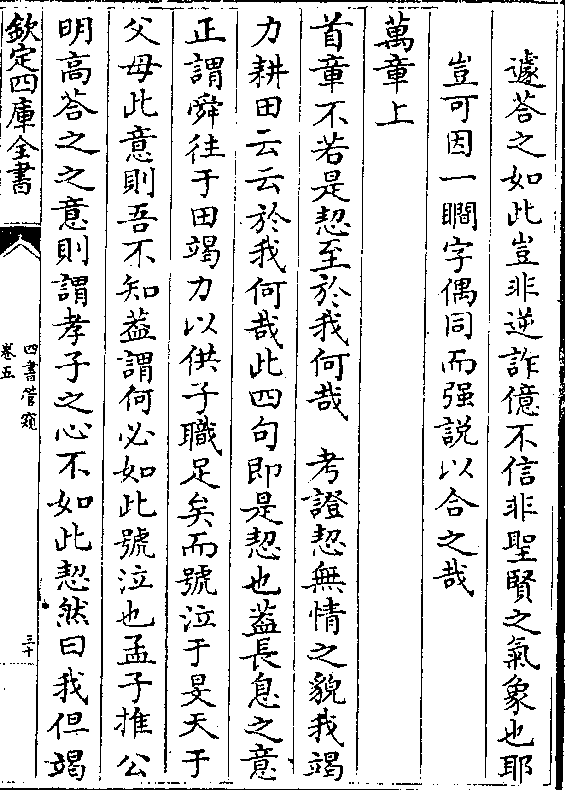 遽荅之如此岂非逆诈亿不信非圣贤之气象也耶
遽荅之如此岂非逆诈亿不信非圣贤之气象也耶岂可因一瞷字偶同而强说以合之哉
万章上
首章不若是恝至于我何哉 考證恝无情之貌我竭
力耕田云云于我何哉此四句即是恝也盖长息之意
正谓舜往于田竭力以供子职足矣而号泣于旻天于
父母此意则吾不知盖谓何必如此号泣也孟子推公
明高荅之之意则谓孝子之心不如此恝然曰我但竭
卷五 第 30b 页 WYG0204-0825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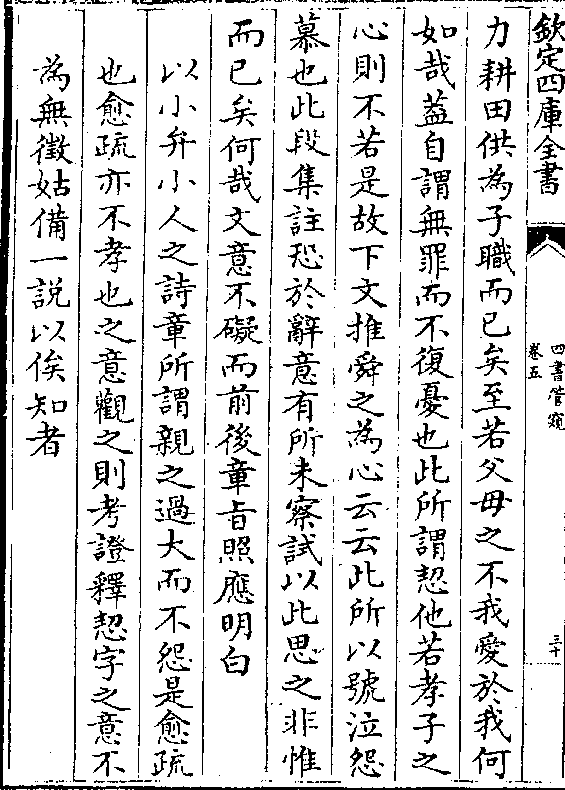 力耕田供为子职而已矣至若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
力耕田供为子职而已矣至若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如哉盖自谓无罪而不复忧也此所谓恝他若孝子之
心则不若是故下文推舜之为心云云此所以号泣怨
慕也此段集注恐于辞意有所未察试以此思之非惟
而已矣何哉文意不碍而前后章旨照应明白
以小弁小人之诗章所谓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
也愈疏亦不孝也之意观之则考證释恝字之意不
为无徵姑备一说以俟知者
卷五 第 31a 页 WYG0204-0825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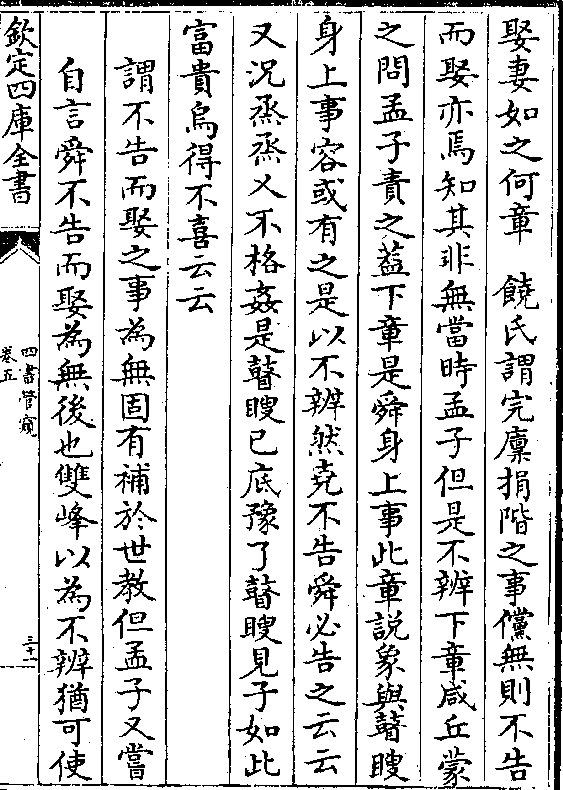 娶妻如之何章 饶氏谓完廪捐阶之事傥无则不告
娶妻如之何章 饶氏谓完廪捐阶之事傥无则不告而娶亦焉知其非无当时孟子但是不辨下章咸丘蒙
之问孟子责之盖下章是舜身上事此章说象与瞽瞍
身上事容或有之是以不辨然尧不告舜必告之云云
又况烝烝又不格奸是瞽瞍已底豫了瞽瞍见子如此
富贵乌得不喜云云
谓不告而娶之事为无固有补于世教但孟子又尝
自言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双峰以为不辨犹可使
卷五 第 31b 页 WYG0204-0825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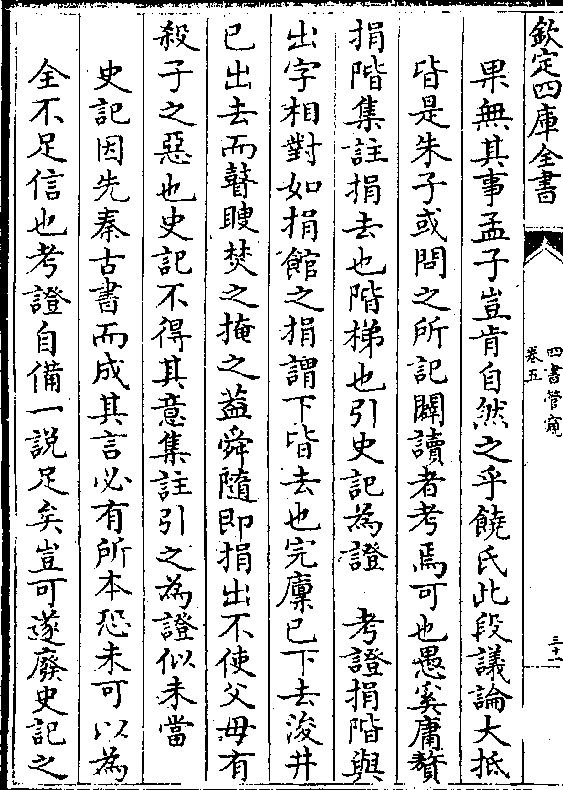 果无其事孟子岂肯自然之乎饶氏此段议论大抵
果无其事孟子岂肯自然之乎饶氏此段议论大抵皆是朱子或问之所记辟读者考焉可也愚奚庸赘
捐阶集注捐去也阶梯也引史记为證 考證捐阶与
出字相对如捐馆之捐谓下皆去也完廪已下去浚井
已出去而瞽瞍焚之掩之盖舜随即捐出不使父母有
杀子之恶也史记不得其意集注引之为證似未当
史记因先秦古书而成其言必有所本恐未可以为
全不足信也考證自备一说足矣岂可遂废史记之
卷五 第 32a 页 WYG0204-0826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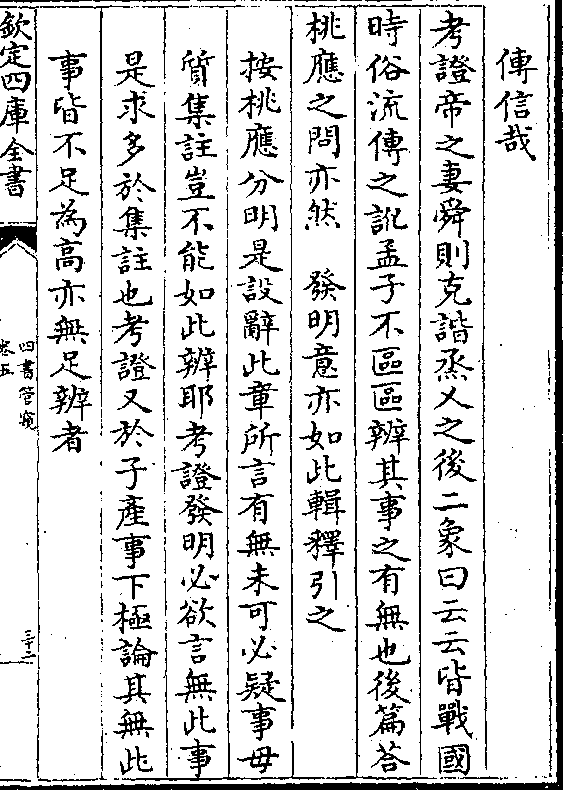 传信哉
传信哉考證帝之妻舜则克谐烝乂之后二象曰云云皆战国
时俗流传之讹孟子不区区辨其事之有无也后篇荅
桃应之问亦然 𤼵明意亦如此辑释引之
按桃应分明是设辞此章所言有无未可必疑事毋
质集注岂不能如此辨耶考證𤼵明必欲言无此事
是求多于集注也考證又于子产事下极论其无此
事皆不足为高亦无足辨者
卷五 第 32b 页 WYG0204-0826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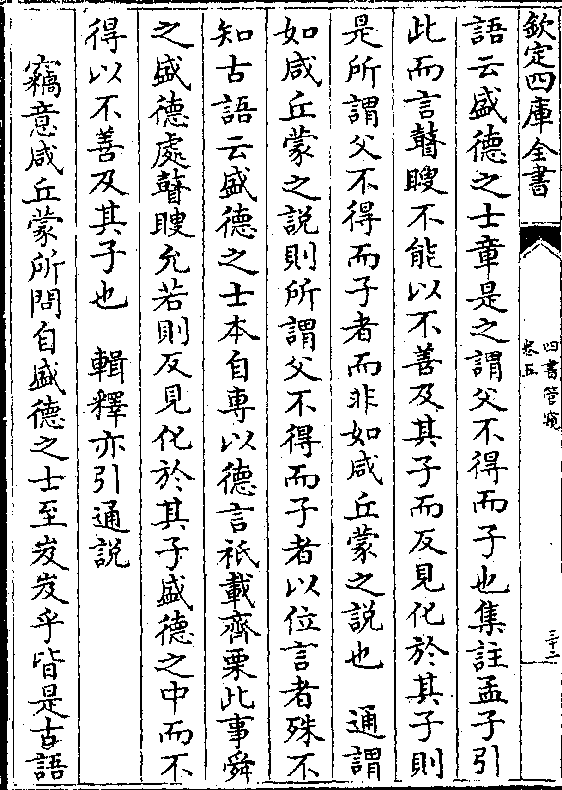 语云盛德之士章是之谓父不得而子也集注孟子引
语云盛德之士章是之谓父不得而子也集注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见化于其子则
是所谓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说也 通谓
如咸丘蒙之说则所谓父不得而子者以位言者殊不
知古语云盛德之士本自专以德言祇载齐栗此事舜
之盛德处瞽瞍允若则反见化于其子盛德之中而不
得以不善及其子也 辑释亦引通说
窃意咸丘蒙所问自盛德之士至岌岌乎皆是古语
卷五 第 33a 页 WYG0204-0826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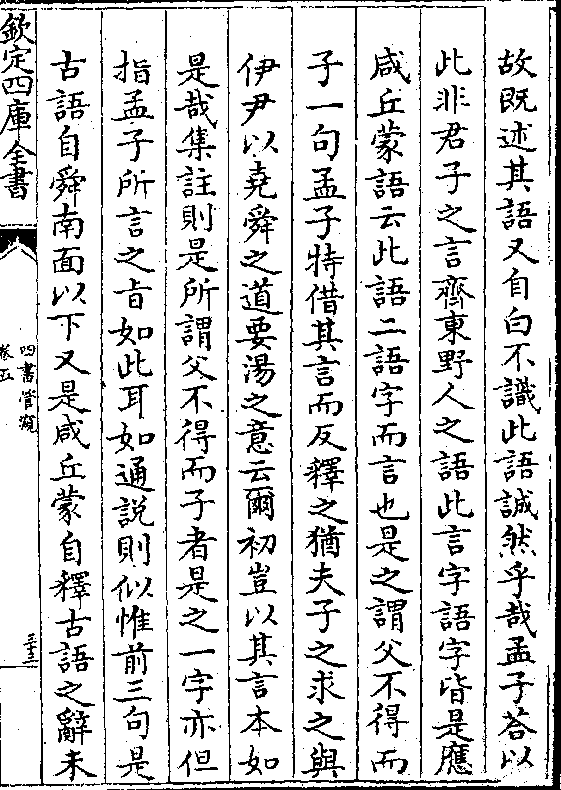 故既述其语又自白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荅以
故既述其语又自白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荅以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此言字语字皆是应
咸丘蒙语云此语二语字而言也是之谓父不得而
子一句孟子特借其言而反释之犹夫子之求之与
伊尹以尧舜之道要汤之意云尔初岂以其言本如
是哉集注则是所谓父不得而子者是之一字亦但
指孟子所言之旨如此耳如通说则似惟前三句是
古语自舜南面以下又是咸丘蒙自释古语之辞未
卷五 第 33b 页 WYG0204-0826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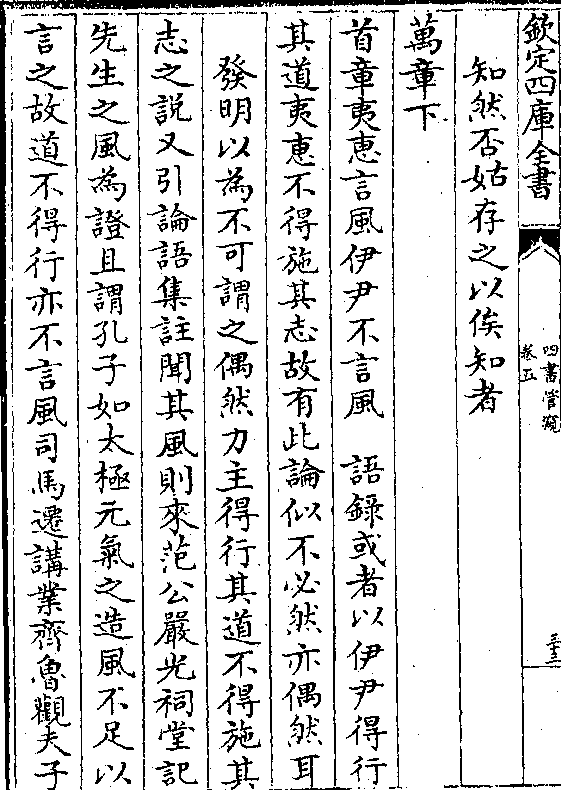 知然否姑存之以俟知者
知然否姑存之以俟知者万章下
首章夷惠言风伊尹不言风 语录或者以伊尹得行
其道夷惠不得施其志故有此论似不必然亦偶然耳
𤼵明以为不可谓之偶然力主得行其道不得施其
志之说又引论语集注闻其风则来范公严光祠堂记
先生之风为證且谓孔子如太极元气之造风不足以
言之故道不得行亦不言风司马迁讲业齐鲁观夫子
卷五 第 34a 页 WYG0204-0827a.png
 之遗风特于齐鲁观之所指有限故亦以风言 辑释
之遗风特于齐鲁观之所指有限故亦以风言 辑释亦引其说
愚谓但当以语录为正若谓道行则不言风然则书
言时乃风诗载十五国风风之所被亦皆不得行其
道者邪集注闻其风则来此正为荅问政而言乃强
说以为远人未被其泽即是道不行于当时之證此
其附会尤为无理且集注朱子所著语录朱子所言
朱子岂不能自引之而烦𤼵明为之引耶太史公范
卷五 第 34b 页 WYG0204-0827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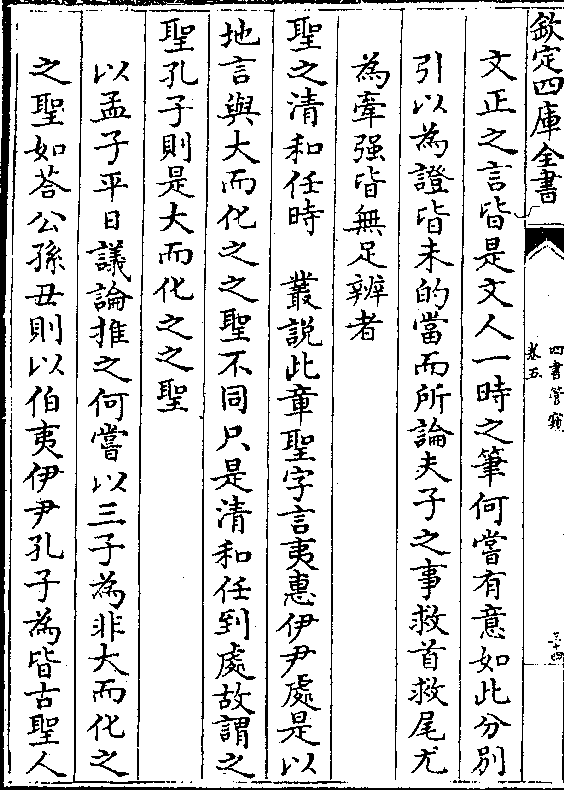 文正之言皆是文人一时之笔何尝有意如此分别
文正之言皆是文人一时之笔何尝有意如此分别引以为證皆未的当而所论夫子之事救首救尾尤
为牵强皆无足辨者
圣之清和任时 丛说此章圣字言夷惠伊尹处是以
地言与大而化之之圣不同只是清和任到处故谓之
圣孔子则是大而化之之圣
以孟子平日议论推之何尝以三子为非大而化之
之圣如荅公孙丑则以伯夷伊尹孔子为皆古圣人
卷五 第 35a 页 WYG0204-0827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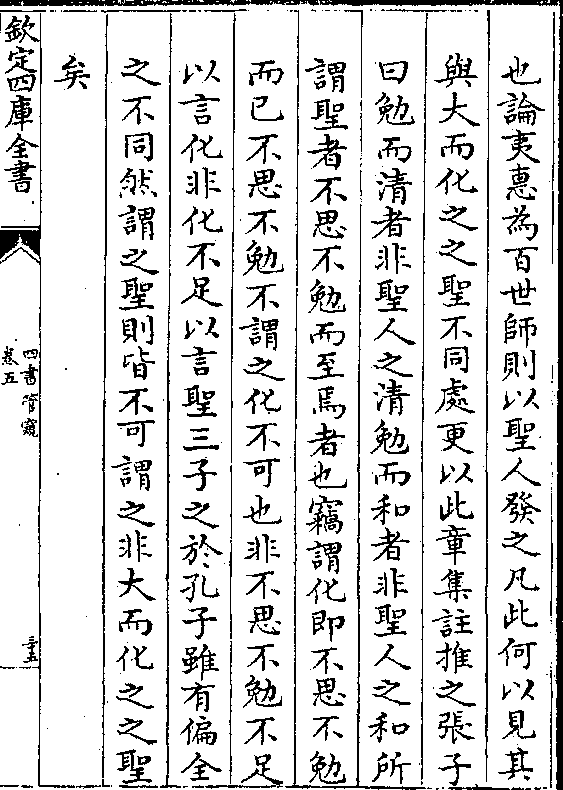 也论夷惠为百世师则以圣人𤼵之凡此何以见其
也论夷惠为百世师则以圣人𤼵之凡此何以见其与大而化之之圣不同处更以此章集注推之张子
曰勉而清者非圣人之清勉而和者非圣人之和所
谓圣者不思不勉而至焉者也窃谓化即不思不勉
而已不思不勉不谓之化不可也非不思不勉不足
以言化非化不足以言圣三子之于孔子虽有偏全
之不同然谓之圣则皆不可谓之非大而化之之圣
矣
卷五 第 35b 页 WYG0204-0827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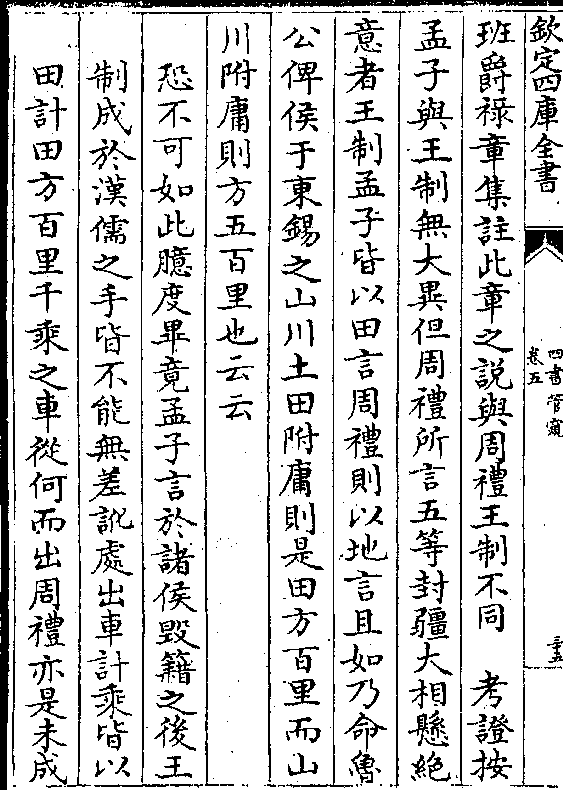 班爵禄章集注此章之说与周礼王制不同 考證按
班爵禄章集注此章之说与周礼王制不同 考證按孟子与王制无大异但周礼所言五等封疆大相悬绝
意者王制孟子皆以田言周礼则以地言且如乃命鲁
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则是田方百里而山
川附庸则方五百里也云云
恐不可如此臆度毕竟孟子言于诸侯毁籍之后王
制成于汉儒之手皆不能无差讹处出车计乘皆以
田计田方百里千乘之车从何而出周礼亦是未成
卷五 第 36a 页 WYG0204-0828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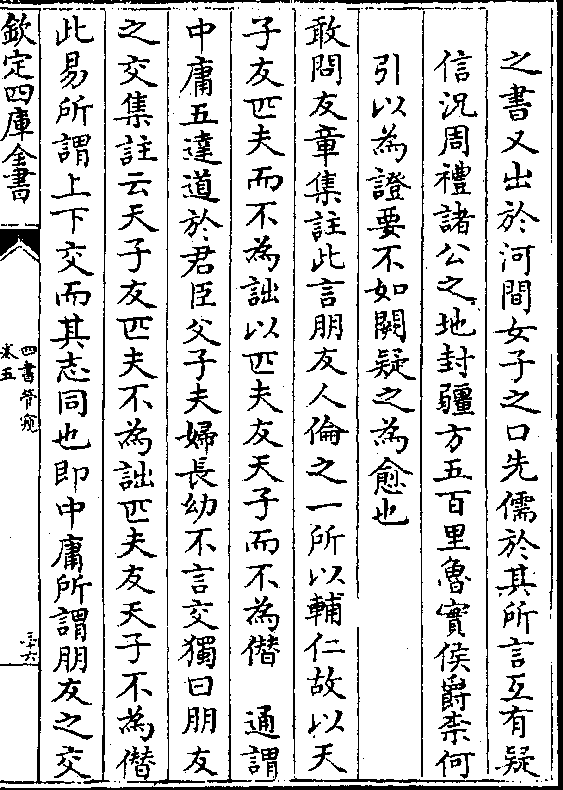 之书又出于河间女子之口先儒于其所言互有疑
之书又出于河间女子之口先儒于其所言互有疑信况周礼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鲁实侯爵柰何
引以为證要不如阙疑之为愈也
敢问友章集注此言朋友人伦之一所以辅仁故以天
子友匹夫而不为诎以匹夫友天子而不为僣 通谓
中庸五达道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不言交独曰朋友
之交集注云天子友匹夫不为诎匹夫友天子不为僣
此易所谓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即中庸所谓朋友之交
卷五 第 36b 页 WYG0204-0828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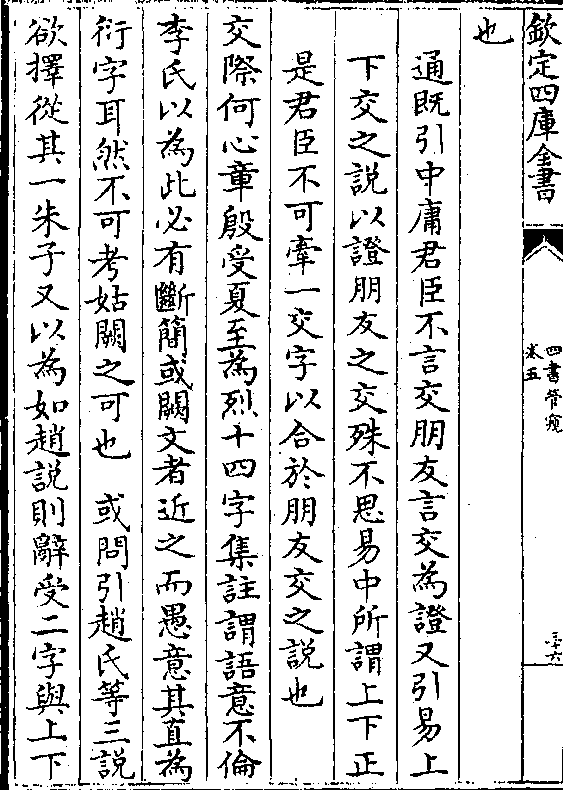 也
也通既引中庸君臣不言交朋友言交为證又引易上
下交之说以證朋友之交殊不思易中所谓上下正
是君臣不可牵一交字以合于朋友交之说也
交际何心章殷受夏至为烈十四字集注谓语意不伦
李氏以为此必有断简或阙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为
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阙之可也 或问引赵氏等三说
欲择从其一朱子又以为如赵说则辞受二字与上下
卷五 第 37a 页 WYG0204-0828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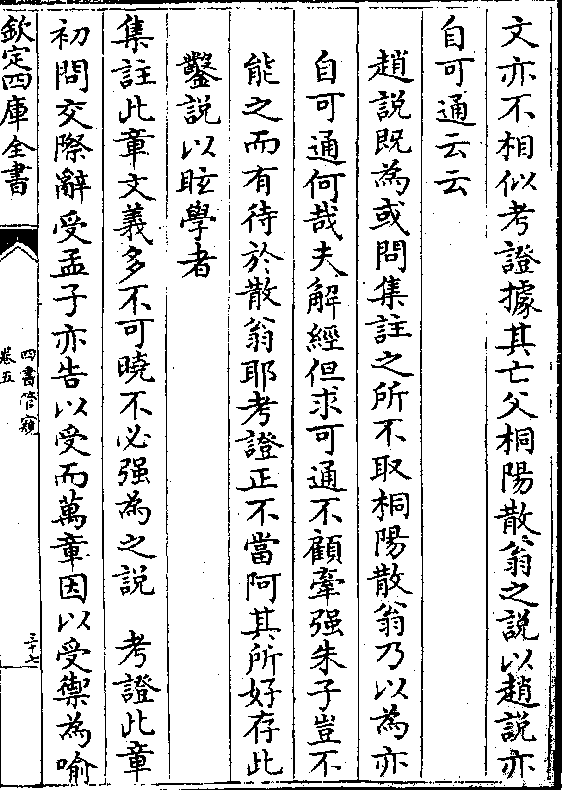 文亦不相似考證据其亡父桐阳散翁之说以赵说亦
文亦不相似考證据其亡父桐阳散翁之说以赵说亦自可通云云
赵说既为或问集注之所不取桐阳散翁乃以为亦
自可通何哉夫解经但求可通不顾牵强朱子岂不
能之而有待于散翁耶考證正不当阿其所好存此
凿说以眩学者
集注此章文义多不可晓不必强为之说 考證此章
初问交际辞受孟子亦告以受而万章因以受禦为喻
卷五 第 37b 页 WYG0204-0828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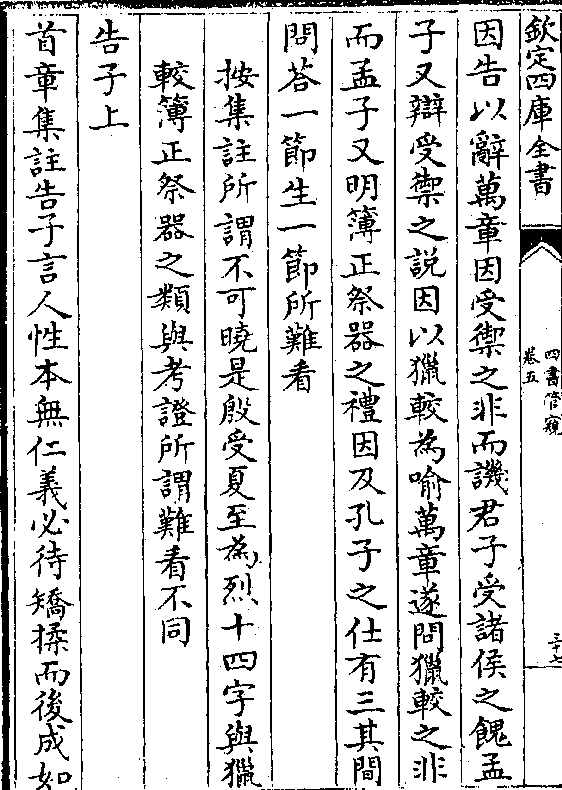 因告以辞万章因受禦之非而讥君子受诸侯之馈孟
因告以辞万章因受禦之非而讥君子受诸侯之馈孟子又辩受禦之说因以猎较为喻万章遂问猎较之非
而孟子又明簿正祭器之礼因及孔子之仕有三其间
问荅一节生一节所难看
按集注所谓不可晓是殷受夏至为烈十四字与猎
较簿正祭器之类与考證所谓难看不同
告子上
首章集注告子言人性本无仁义必待矫揉而后成如
卷五 第 38a 页 WYG0204-0829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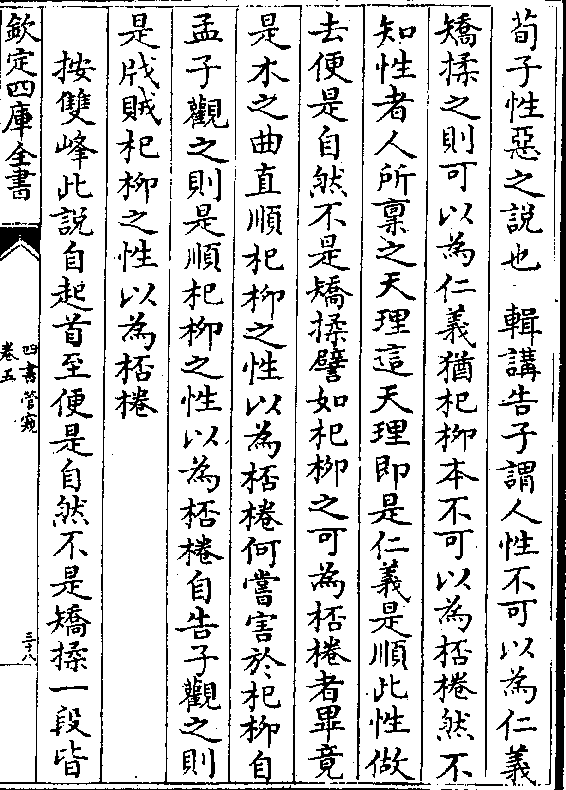 荀子性恶之说也 辑讲告子谓人性不可以为仁义
荀子性恶之说也 辑讲告子谓人性不可以为仁义矫揉之则可以为仁义犹把柳本不可以为杯棬然不
知性者人所禀之天理这天理即是仁义是顺此性做
去便是自然不是矫揉譬如把柳之可为杯棬者毕竟
是木之曲直顺把柳之性以为杯棬何尝害于把柳自
孟子观之则是顺把柳之性以为杯棬自告子观之则
是戕贼把柳之性以为杯棬
按双峰此说自起首至便是自然不是矫揉一段皆
卷五 第 38b 页 WYG0204-0829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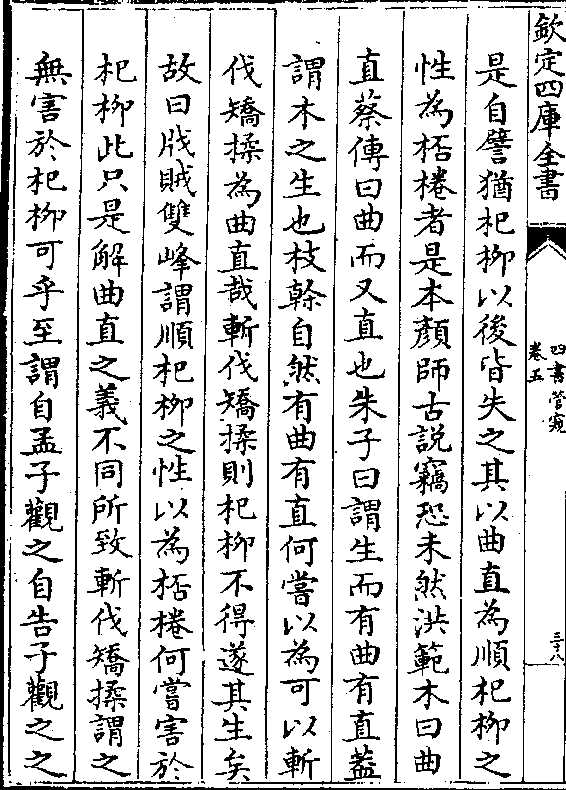 是自譬犹把柳以后皆失之其以曲直为顺把柳之
是自譬犹把柳以后皆失之其以曲直为顺把柳之性为杯棬者是本颜师古说窃恐未然洪范未曰曲
直蔡傅曰曲而又直也朱子曰谓生而有曲有直盖
谓木之生也枝干自然有曲有直何尝以为可以斩
伐矫揉为曲直哉斩伐矫揉则把柳不得遂其生矣
故曰戕贼双峰谓顺把柳之性以为杯棬何尝害于
把柳此只是解曲直之义不同所致斩伐矫揉谓之
无害于把柳可乎至谓自孟子观之自告子观之之
卷五 第 39a 页 WYG0204-0829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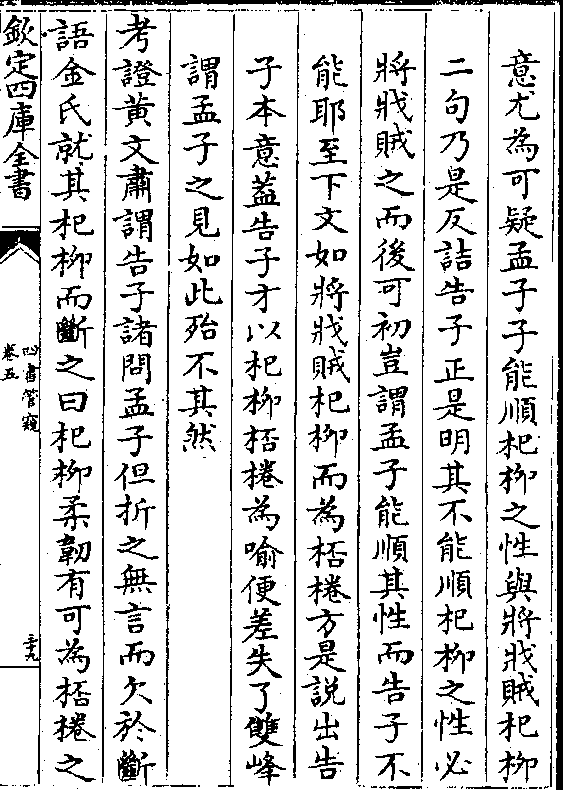 意尤为可疑孟子子能顺把柳之性与将戕贼把柳
意尤为可疑孟子子能顺把柳之性与将戕贼把柳二句乃是反诘告子正是明其不能顺把柳之性必
将戕贼之而后可初岂谓孟子能顺其性而告子不
能耶至下文如将戕贼把柳而为杯棬方是说出告
子本意盖告子才以把柳杯棬为喻便差失了双峰
谓孟子之见如此殆不其然
考證黄文肃谓告子诸问孟子但折之无言而欠于断
语金氏就其把柳而断之曰把柳柔韧有可为杯棬之
卷五 第 39b 页 WYG0204-0829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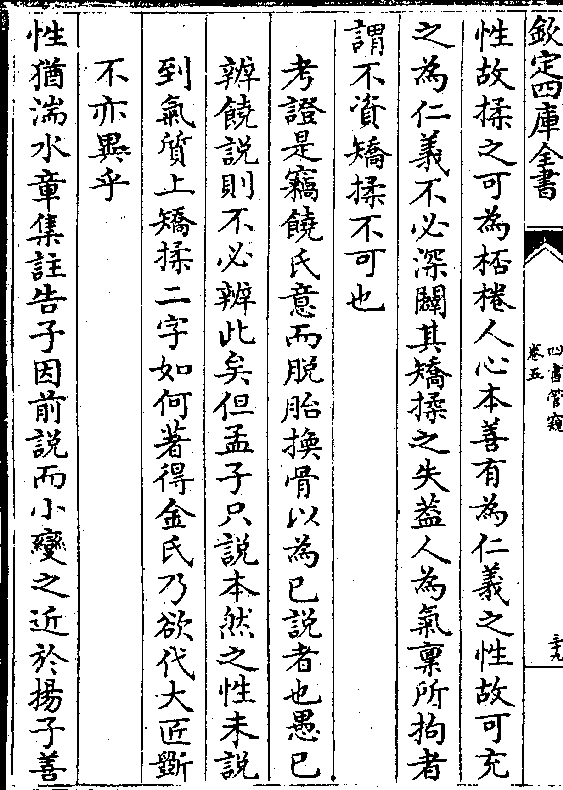 性故揉之可为杯棬人心本善有为仁义之性故可充
性故揉之可为杯棬人心本善有为仁义之性故可充之为仁义不必深辟其矫揉之失盖人为气禀所拘者
谓不资矫揉不可也
考證是窃饶氏意而脱胎换骨以为己说者也愚己
辨饶说则不必辨此矣但孟子只说本然之性未说
到气质上矫揉二字如何著得金氏乃欲代大匠斲
不亦异乎
性犹湍水章集注告子因前说而小变之近于扬子善
卷五 第 40a 页 WYG0204-0830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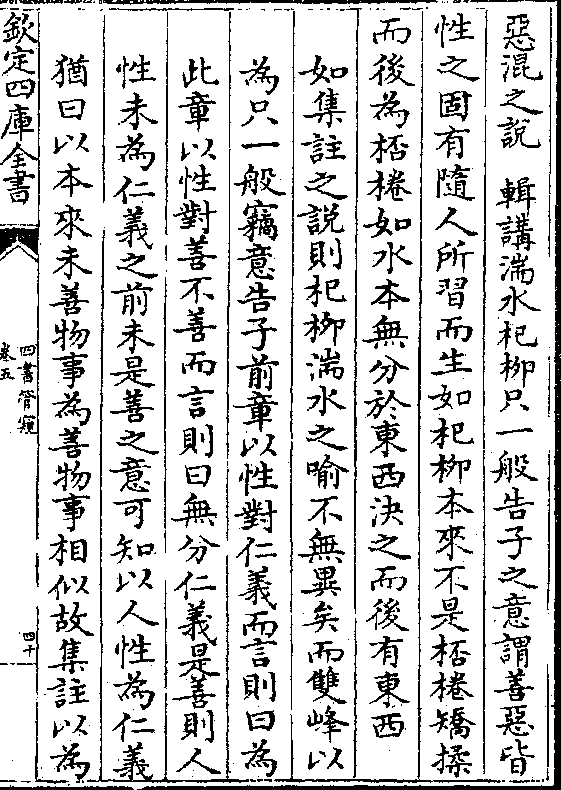 恶混之说 辑讲湍水杞柳只一般告子之意谓善恶皆
恶混之说 辑讲湍水杞柳只一般告子之意谓善恶皆性之固有随人所习而生如把柳本来不是杯棬矫揉
而后为杯棬如水本无分于东西决之而后有东西
如集注之说则把柳湍水之喻不无异矣而双峰以
为只一般窃意告子前章以性对仁义而言则曰为
此章以性对善不善而言则曰无分仁义是善则人
性未为仁义之前未是善之意可知以人性为仁义
犹曰以本来未善物事为善物事相似故集注以为
卷五 第 40b 页 WYG0204-0830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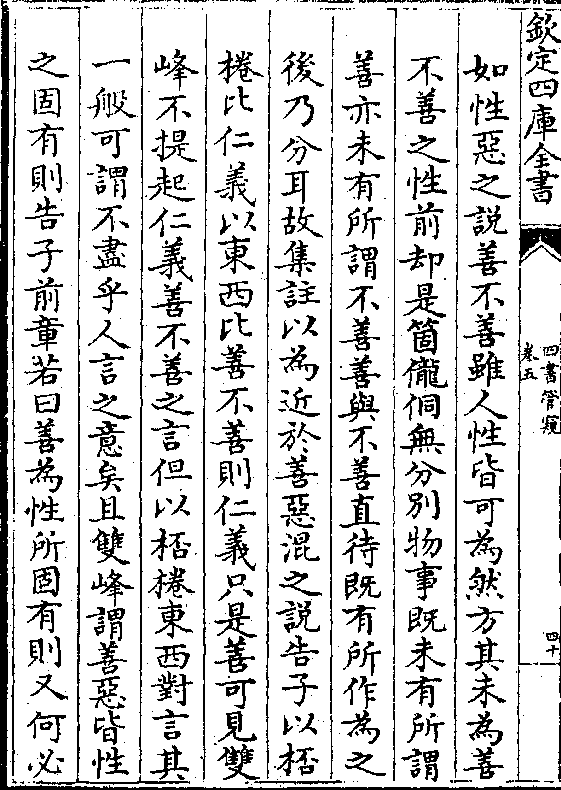 如性恶之说善不善虽人性皆可为然方其未为善
如性恶之说善不善虽人性皆可为然方其未为善不善之性前却是个儱侗无分别物事既未有所谓
善亦未有所谓不善善与不善直待既有所作为之
后乃分耳故集注以为近于善恶混之说告子以杯
棬比仁义以东西比善不善则仁义只是善可见双
峰不提起仁义善不善之言但以杯棬东西对言其
一般可谓不尽乎人言之意矣且双峰谓善恶皆性
之固有则告子前章若曰善为性所固有则又何必
卷五 第 41a 页 WYG0204-0830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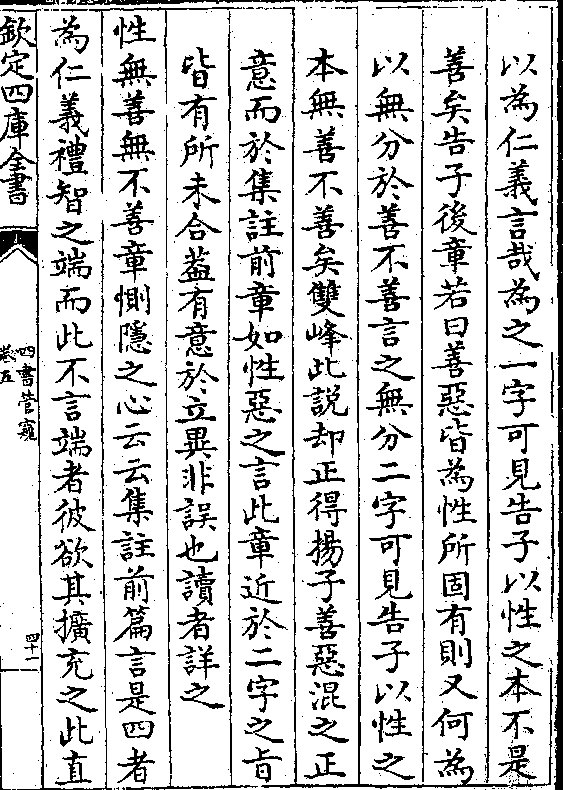 以为仁义言哉为之一字可见告子以性之本不是
以为仁义言哉为之一字可见告子以性之本不是善矣告子后章若曰善恶皆为性所固有则又何为
以无分于善不善言之无分二字可见告子以性之
本无善不善矣双峰此说却正得扬子善恶混之正
意而于集注前章如性恶之言此章近于二字之旨
皆有所未合盖有意于立异非误也读者详之
性无善无不善章恻隐之心云云集注前篇言是四者
为仁义礼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扩充之此直
卷五 第 41b 页 WYG0204-0830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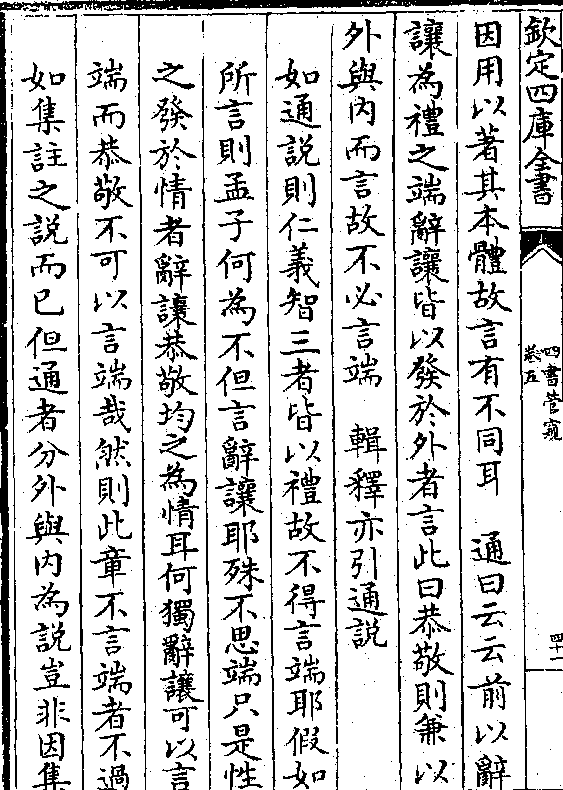 因用以著其本体故言有不同耳 通曰云云前以辞
因用以著其本体故言有不同耳 通曰云云前以辞让为礼之端辞让皆以𤼵于外者言此曰恭敬则兼以
外与内而言故不必言端 辑释亦引通说
如通说则仁义智三者皆以礼故不得言端耶假如
所言则孟子何为不但言辞让耶殊不思端只是性
之𤼵于情者辞让恭敬均之为情耳何独辞让可以言
端而恭敬不可以言端哉然则此章不言端者不过
如集注之说而已但通者分外与内为说岂非因集
卷五 第 42a 页 WYG0204-0831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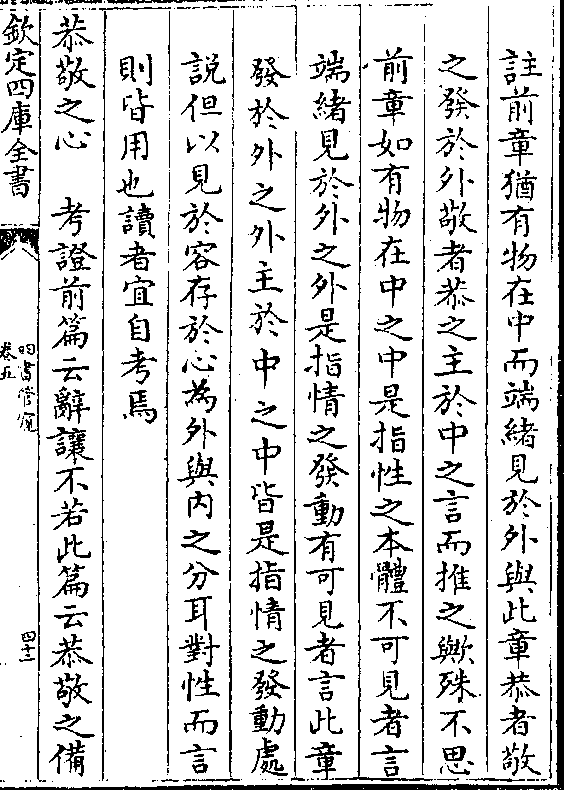 注前章犹有物在中而端绪见于外与此章恭者敬
注前章犹有物在中而端绪见于外与此章恭者敬之𤼵于外敬者恭之主于中之言而推之欤殊不思
前章如有物在中之中是指性之本体不可见者言
端绪见于外之外是指情之𤼵动有可见者言此章
发于外之外主于中之中皆是指情之发动处
说但以见于容存于心为外与内之分耳对性而言
则皆用也读者宜自考焉
恭敬之心 考證前篇云辞让不若此篇云恭敬之备
卷五 第 42b 页 WYG0204-0831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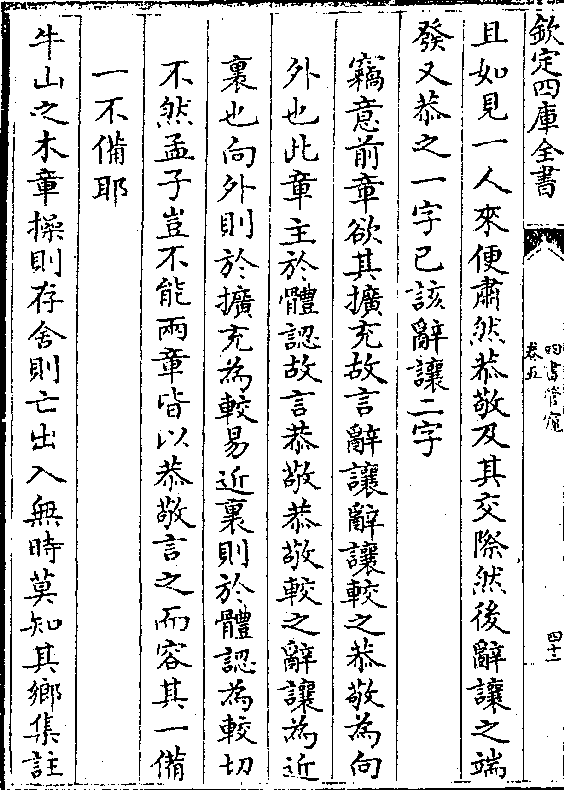 且如见一人来便肃然恭敬及其交际然后辞让之端
且如见一人来便肃然恭敬及其交际然后辞让之端𤼵又恭之一字已该辞让二字
窃意前章欲其扩充故言辞让辞让较之恭敬为向
外也此章主于体认故言恭敬恭敬较之辞让为近
里也向外则于扩充为较易近里则于体认为较切
不然孟子岂不能两章皆以恭敬言之而容其一备
一不备耶
牛山之木章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集注
卷五 第 43a 页 WYG0204-0831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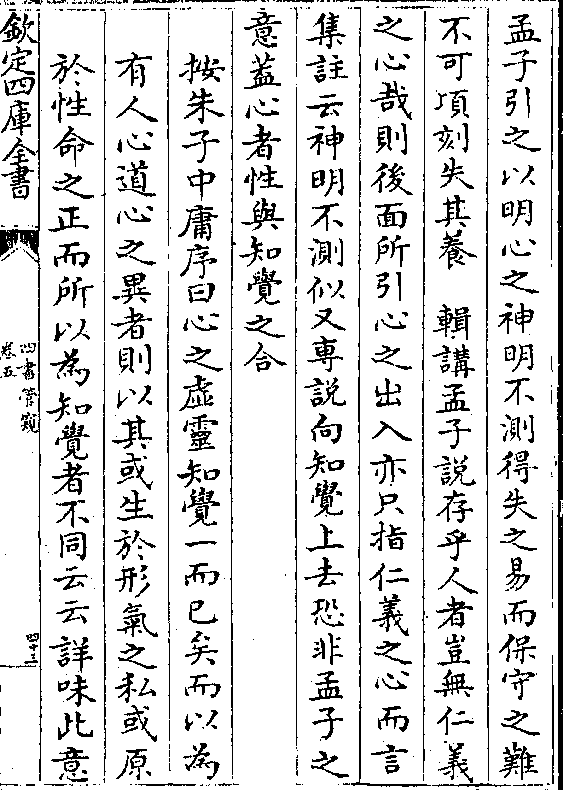 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测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难
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测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难不可顷刻失其养 辑讲孟子说存乎人者岂无仁义
之心哉则后面所引心之出入亦只指仁义之心而言
集注云神明不测似又专说向知觉上去恐非孟子之
意盖心者性与知觉之合
按朱子中庸序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
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
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云云详味此意
卷五 第 43b 页 WYG0204-0831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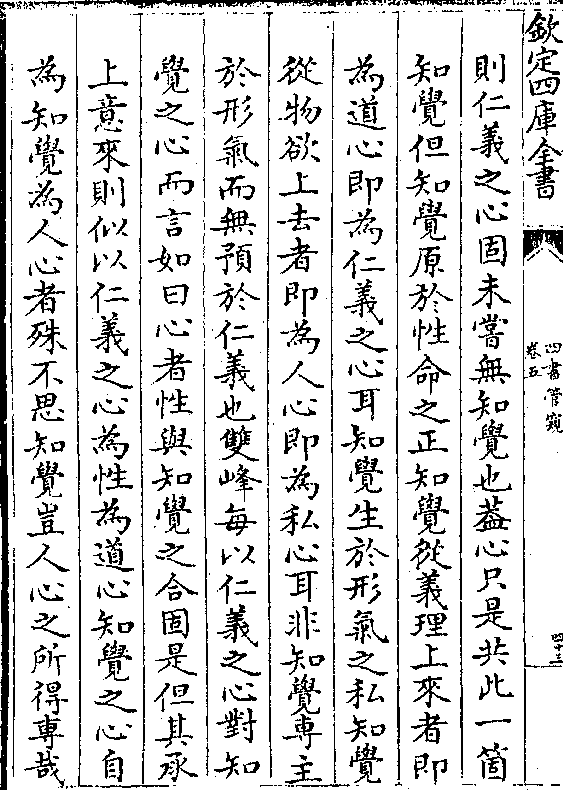 则仁义之心固未尝无知觉也盖心只是共此一个
则仁义之心固未尝无知觉也盖心只是共此一个知觉但知觉原于性命之正知觉从义理上来者即
为道心即为仁义之心耳知觉生于形气之私知觉
从物欲上去者即为人心即为私心耳非知觉专主
于形气而无预于仁义也双峰每以仁义之心对知
觉之心而言如曰心者性与知觉之合固是但其承
上意来则似以仁义之心为性为道心知觉之心自
为知觉为人心者殊不思知觉岂人心之所得专哉
卷五 第 44a 页 WYG0204-0832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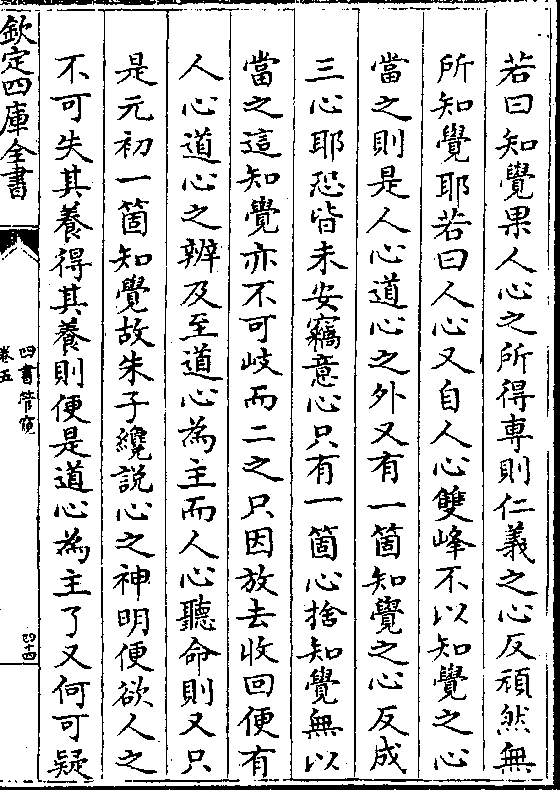 若曰知觉果人心之所得专则仁义之心反顽然无
若曰知觉果人心之所得专则仁义之心反顽然无所知觉耶若曰人心又自人心双峰不以知觉之心
当之则是人心道心之外又有一个知觉之心反成
三心耶恐皆未安窃意心只有一个心舍知觉无以
当之这知觉亦不可岐而二之只因放去收回便有
人心道心之辨及至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则又只
是元初一个知觉故朱子才说心之神明便欲人之
不可失其养得其养则便是道心为主了又何可疑
卷五 第 44b 页 WYG0204-0832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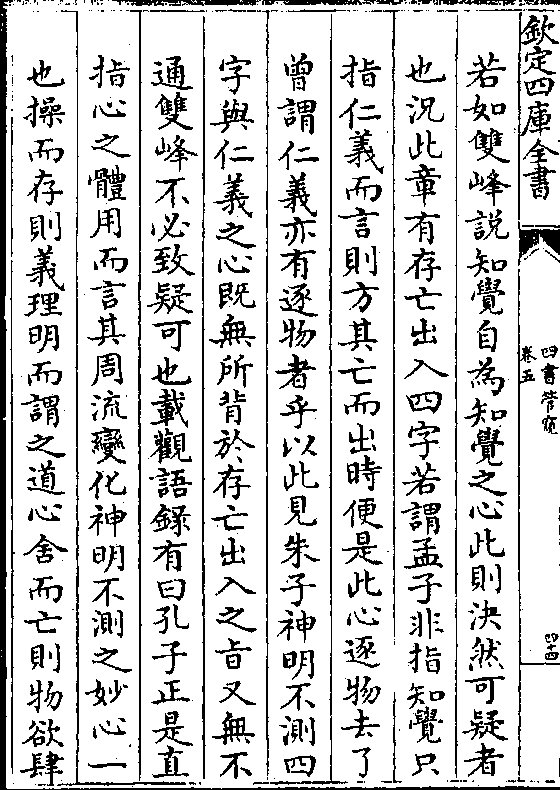 若如双峰说知觉自为知觉之心此则决然可疑者
若如双峰说知觉自为知觉之心此则决然可疑者也况此章有存亡出入四字若谓孟子非指知觉只
指仁义而言则方其亡而出时便是此心逐物去了
曾谓仁义亦有逐物者乎以此见朱子神明不测四
字与仁义之心既无所背于存亡出入之旨又无不
通双峰不必致疑可也载观语录有曰孔子正是直
指心之体用而言其周流变化神明不测之妙心一
也操而存则义理明而谓之道心舍而亡则物欲肆
卷五 第 45a 页 WYG0204-0832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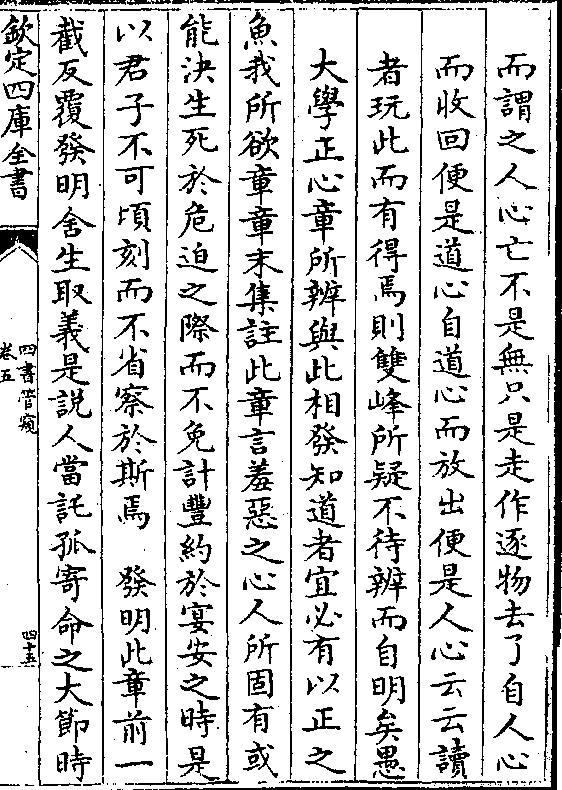 而谓之人心亡不是无只是走作逐物去了自人心
而谓之人心亡不是无只是走作逐物去了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云云读
者玩此而有得焉则双峰所疑不待辨而自明矣愚
大学正心章所辨与此相𤼵知道者宜必有以正之
鱼我所欲章章末集注此章言羞恶之心人所固有或
能决生死于危迫之际而不免计丰约于宴安之时是
以君子不可顷刻而不省察于斯焉 𤼵明此章前一
截反覆𤼵明舍生取义是说人当托孤寄命之大节时
卷五 第 45b 页 WYG0204-0832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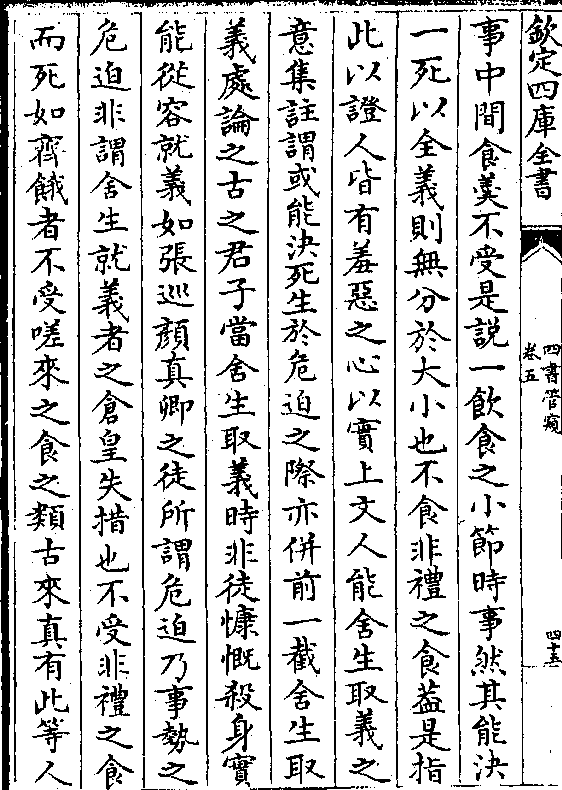 事中间食羹不受是说一饮食之小节时事然其能决
事中间食羹不受是说一饮食之小节时事然其能决一死以全义则无分于大小也不食非礼之食盖是指
此以證人皆有羞恶之心以实上文人能舍生取义之
意集注谓或能决死生于危迫之际亦并前一截舍生取
义处论之古之君子当舍生取义时非徒慷慨杀身实
能从容就义如张巡颜真卿之徒所谓危迫乃事势之
危迫非谓舍生就义者之仓皇失措也不受非礼之食
而死如齐饿者不受嗟来之食之类古来真有此等人
卷五 第 46a 页 WYG0204-0833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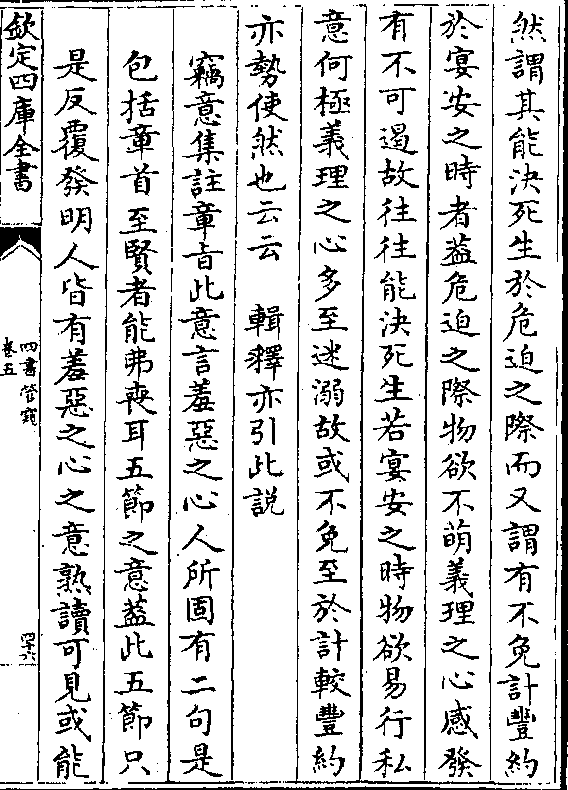 然谓其能决死生于危迫之际而又谓有不免计丰约
然谓其能决死生于危迫之际而又谓有不免计丰约于宴安之时者盖危迫之际物欲不萌义理之心感𤼵
有不可遏故往往能决死生若宴安之时物欲易行私
意何极义理之心多至迷溺故或不免至于计较丰约
亦势使然也云云 辑释亦引此说
窃意集注章旨此意言羞恶之心人所固有二句是
包括章首至贤者能弗丧耳五节之意盖此五节只
是反覆𤼵明人皆有羞恶之心之意熟读可见或能
卷五 第 46b 页 WYG0204-0833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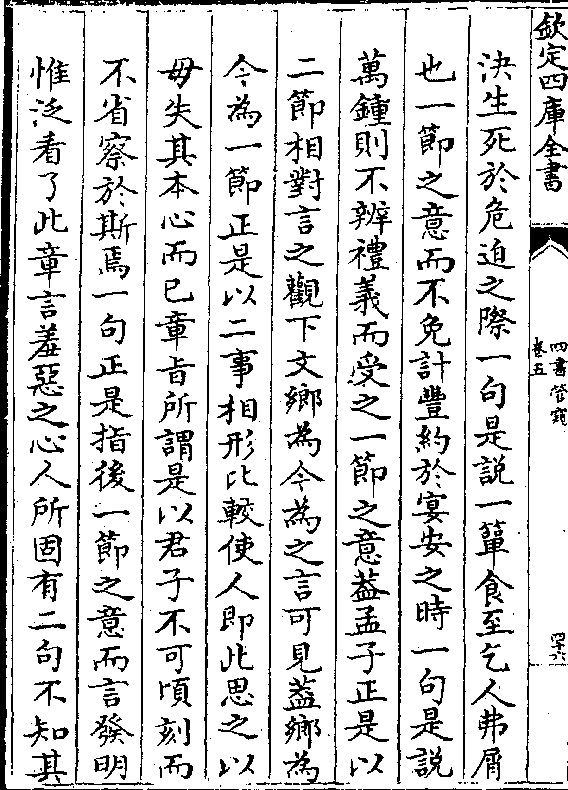 决生死于危迫之际一句是说一箪食至乞人弗屑
决生死于危迫之际一句是说一箪食至乞人弗屑也一节之意而不免计丰约于宴安之时一句是说
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一节之意盖孟子正是以
二节相对言之观下文乡为今为之言可见盖乡为
今为一节正是以二事相形比较使人即此思之以
毋失其本心而已章旨所谓是以君子不可顷刻而
不省察于斯焉一句正是指后一节之意而言𤼵明
惟泛看了此章言羞恶之心人所固有二句不知其
卷五 第 47a 页 WYG0204-0833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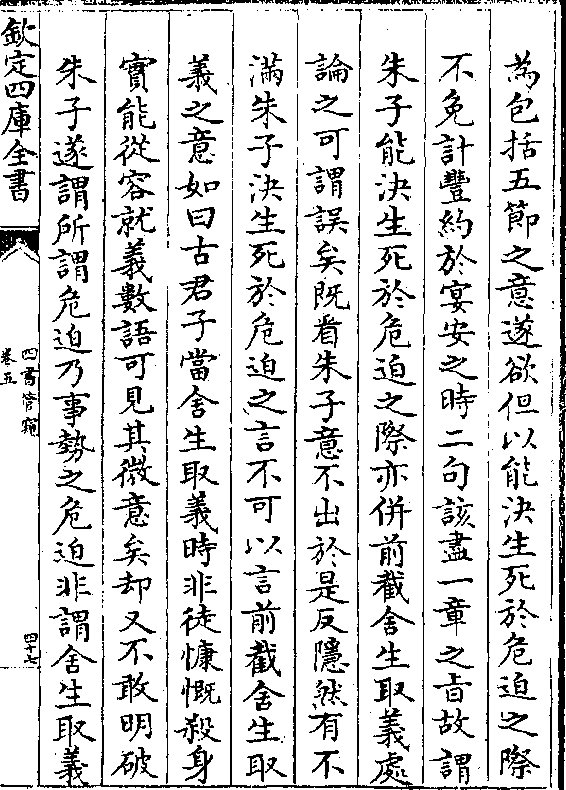 为包括五节之意遂欲但以能决生死于危迫之际
为包括五节之意遂欲但以能决生死于危迫之际不免计丰约于宴安之时二句该尽一章之旨故谓
朱子能决生死于危迫之际亦并前截舍生取义处
论之可谓误矣既看朱子意不出于是反隐然有不
满朱子决生死于危迫之言不可以言前截舍生取
义之意如曰古君子当舍生取义时非徒慷慨杀身
实能从容就义数语可见其微意矣却又不敢明破
朱子遂谓所谓危迫乃事势之危迫非谓舍生取义
卷五 第 47b 页 WYG0204-0833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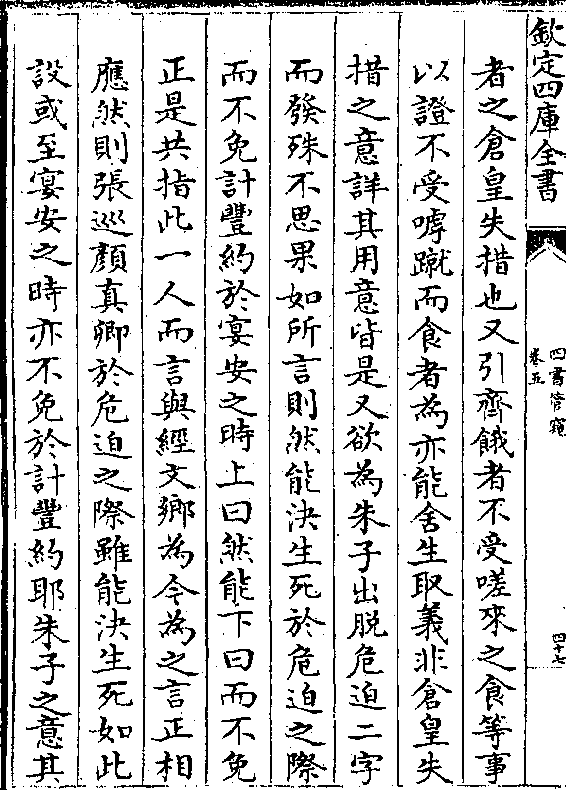 者之仓皇失措也又引齐饿者不受嗟来之食等事
者之仓皇失措也又引齐饿者不受嗟来之食等事以證不受嘑蹴而食者为亦能舍生取义非仓皇失
措之意详其用意皆是又欲为朱子出脱危迫二字
而𤼵殊不思果如所言则然能决生死于危迫之际
而不免计丰约于宴安之时上曰然能下曰而不免
正是共指此一人而言与经文乡为今为之言正相
应然则张巡颜真卿于危迫之际虽能决生死如此
设或至宴安之时亦不免于计丰约耶朱子之意其
卷五 第 48a 页 WYG0204-0834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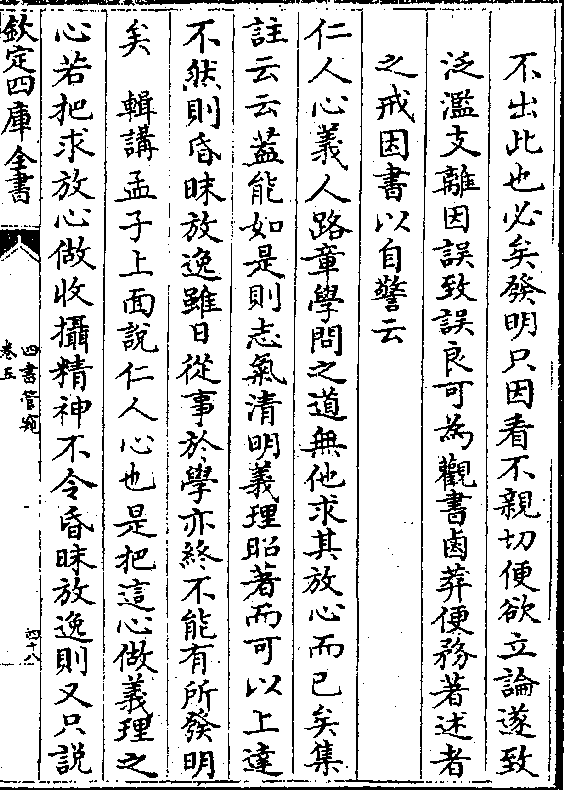 不出此也必矣𤼵明只因看不亲切便欲立论遂致
不出此也必矣𤼵明只因看不亲切便欲立论遂致泛滥支离因误致误良可为观书卤莽便务著述者
之戒因书以自警云
仁人心义人路章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集
注云云盖能如是则志气清明义理昭著而可以上达
不然则昏昩放逸虽日从事于学亦终不能有所𤼵明
矣 辑讲孟子上面说仁人心也是把这心做义理之
心若把求放心做收摄精神不令昏昧放逸则又只说
卷五 第 48b 页 WYG0204-0834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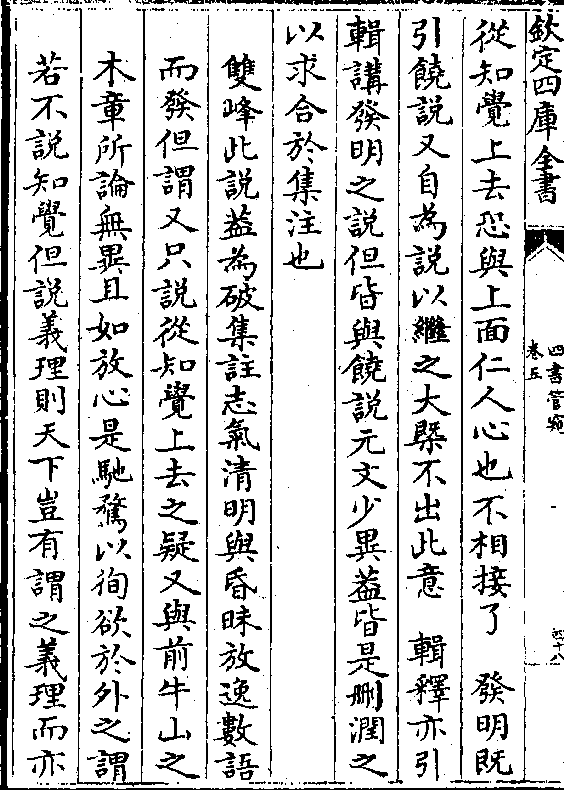 从知觉上去恐与上面仁人心也不相接了 𤼵明既
从知觉上去恐与上面仁人心也不相接了 𤼵明既引饶说又自为说以继之大槩不出此意 辑释亦引
辑讲𤼵明之说但皆与饶说元文少异盖皆是删润之
以求合于集注也
双峰此说盖为破集注志气清明与昏昧放逸数语
而𤼵但谓又只说从知觉上去之疑又与前牛山之
木章所论无异且如放心是驰鹜以徇欲于外之谓
若不说知觉但说义理则天下岂有谓之义理而亦
卷五 第 49a 页 WYG0204-0834c.png
 徇欲放逸于外者耶以此见得虽说从知觉上去却
徇欲放逸于外者耶以此见得虽说从知觉上去却于义理放逸之意两无所妨其详已于前章见之此
不再述按此章四段所谓心字初焉仁人心之心固
不待论第二节放其心不知求之心是承人心得失
而言亦皆指仁而言无疑第三节有放心不知求集
注谓上并言仁义而此下专论求放心者能求放心
则不违乎仁而义在其中矣何尝以心为不指仁而
言耶既曰此下专论求放心则包第三第四节二心
卷五 第 49b 页 WYG0204-0834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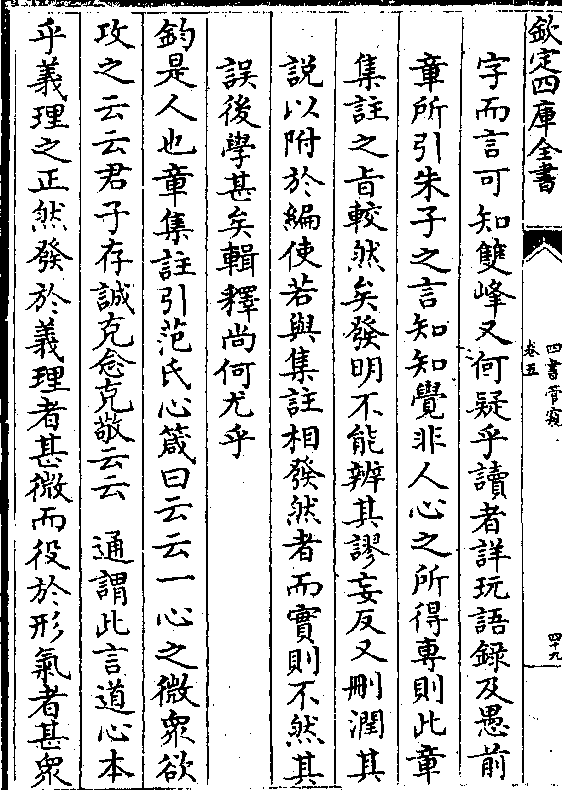 字而言可知双峰又何疑乎读者详玩语录及愚前
字而言可知双峰又何疑乎读者详玩语录及愚前章所引朱子之言知知觉非人心之所得专则此章
集注之旨较然矣𤼵明不能辨其谬妄反又删润其
说以附于编使若与集注相𤼵然者而实则不然其
误后学甚矣辑释尚何尤乎
钧是人也章集注引范氏心箴曰云云一心之微众欲
攻之云云君子存诚克念克敬云云通谓此言道心本
乎义理之正然𤼵于义理者甚微而役于形气者甚众
卷五 第 50a 页 WYG0204-0835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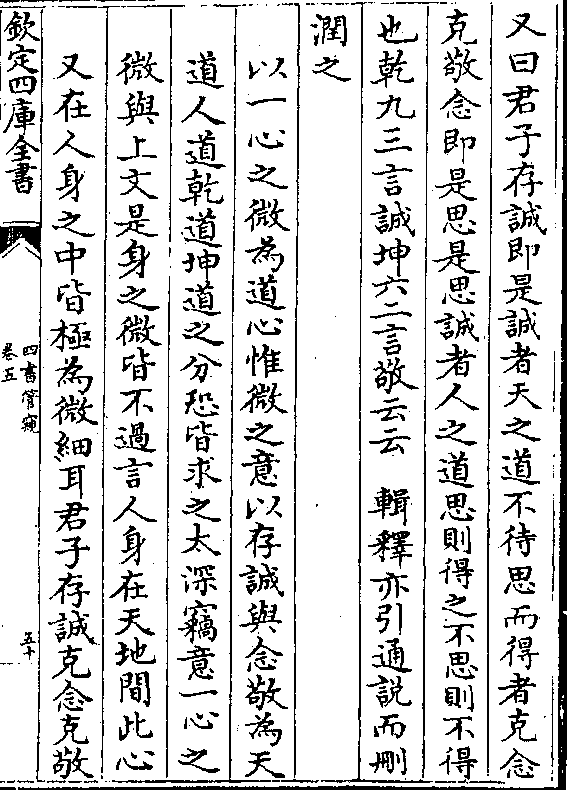 又曰君子存诚即是诚者天之道不待思而得者克念
又曰君子存诚即是诚者天之道不待思而得者克念克敬念即是思是思诚者人之道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
也乾九三言诚坤六二言敬云云 辑释亦引通说而删
润之
以一心之微为道心惟微之意以存诚与念敬为天
道人道乾道坤道之分恐皆求之太深窃意一心之
微与上文是身之微皆不过言人身在天地间此心
又在人身之中皆极为微细耳君子存诚克念克敬
卷五 第 50b 页 WYG0204-0835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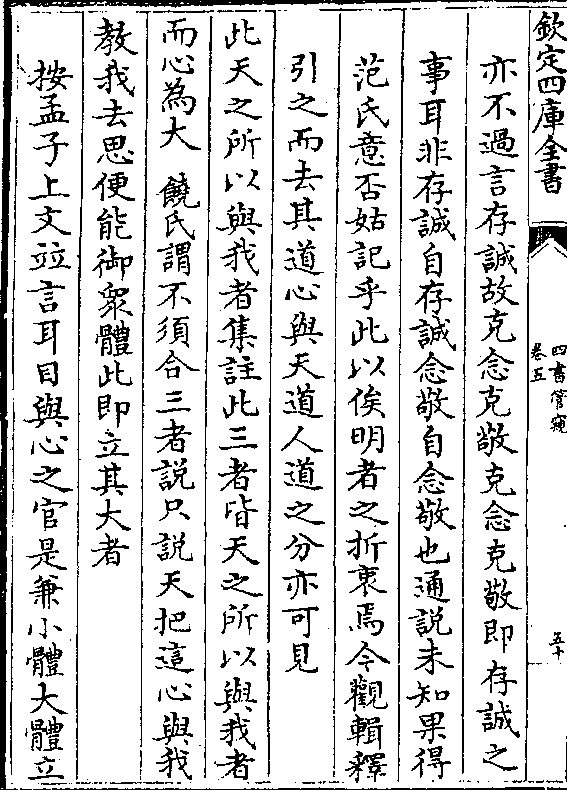 亦不过言存诚故克念克敬克念克敬即存诚之
亦不过言存诚故克念克敬克念克敬即存诚之事耳非存诚自存诚念敬自念敬也通说未知果得
范氏意否姑记乎此以俟明者之折衷焉今观辑释
引之而去其道心与天道人道之分亦可见
此天之所以与我者集注此三者皆天之所以与我者
而心为大 饶氏谓不须合三者说只说天把这心与我
教我去思便能御众体此即立其大者
按孟子上文并言耳目与心之官是兼小体大体立
卷五 第 51a 页 WYG0204-0835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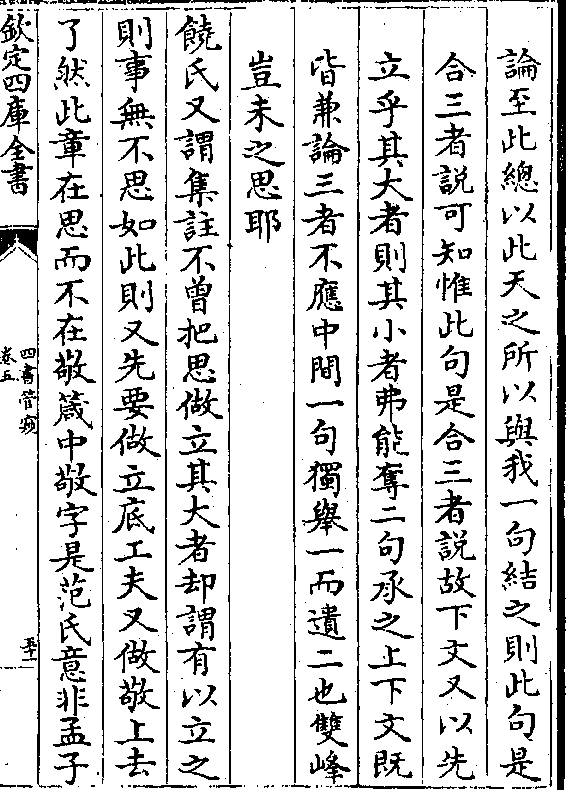 论至此总以此天之所以与我一句结之则此句是
论至此总以此天之所以与我一句结之则此句是合三者说可知惟此句是合三者说故下文又以先
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二句承之上下文既
皆兼论三者不应中间一句独举一而遗二也双峰
岂未之思耶
饶氏又谓集注不曾把思做立其大者却谓有以立之
则事无不思如此则又先要做立底工夫又做敬上去
了然此章在思而不在敬箴中敬字是范氏意非孟子
卷五 第 51b 页 WYG0204-0835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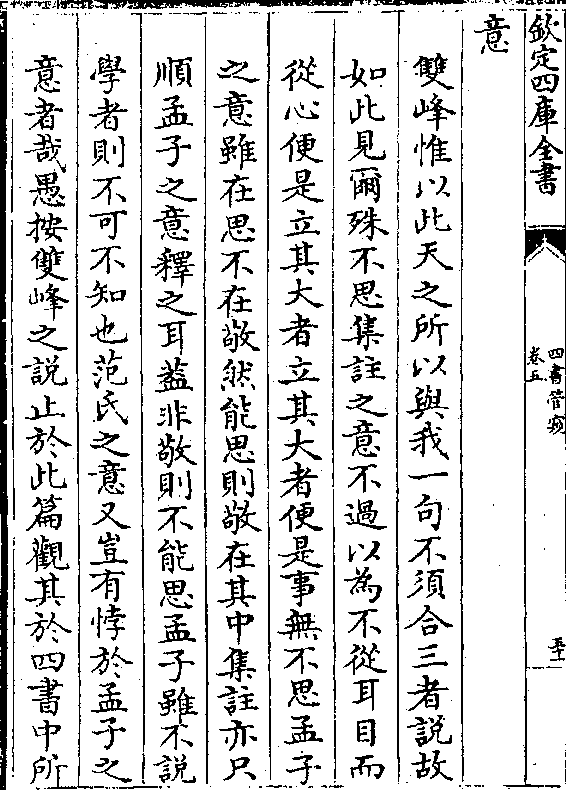 意
意双峰惟以此天之所以与我一句不须合三者说故
如此见尔殊不思集注之意不过以为不从耳目而
从心便是立其大者立其大者便是事无不思孟子
之意虽在思不在敬然能思则敬在其中集注亦只
顺孟子之意释之耳盖非敬则不能思孟子虽不说
学者则不可不知也范氏之意又岂有悖于孟子之
意者哉愚按双峰之说止于此篇观其于四书中所
卷五 第 52a 页 WYG0204-0836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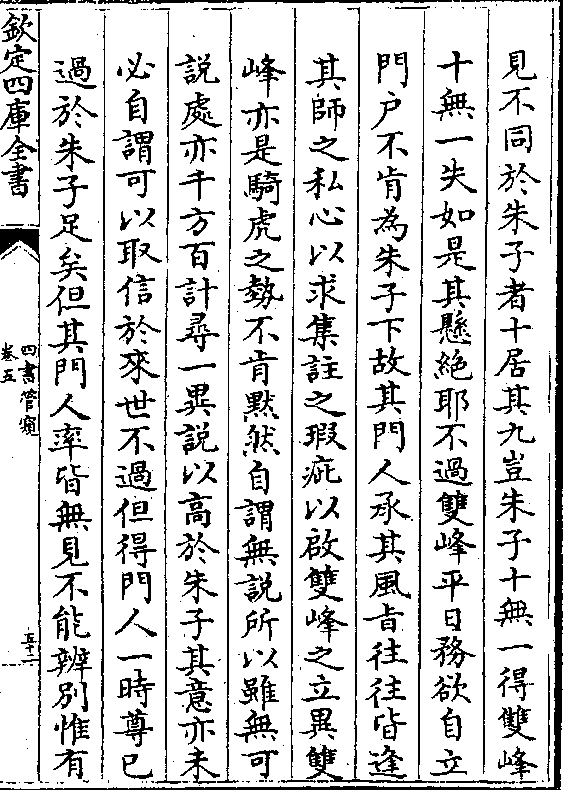 见不同于朱子者十居其九岂朱子十无一得双峰
见不同于朱子者十居其九岂朱子十无一得双峰十无一失如是其悬绝耶不过双峰平日务欲自立
门户不肯为朱子下故其门人承其风旨往往皆逢
其师之私心以求集注之瑕疵以启双峰之立异双
峰亦是骑虎之势不肯默然自谓无说所以虽无可
说处亦千方百计寻一异说以高于朱子其意亦未
必自谓可以取信于来世不过但得门人一时尊己
过于朱子足矣但其门人率皆无见不能辨别惟有
卷五 第 52b 页 WYG0204-0836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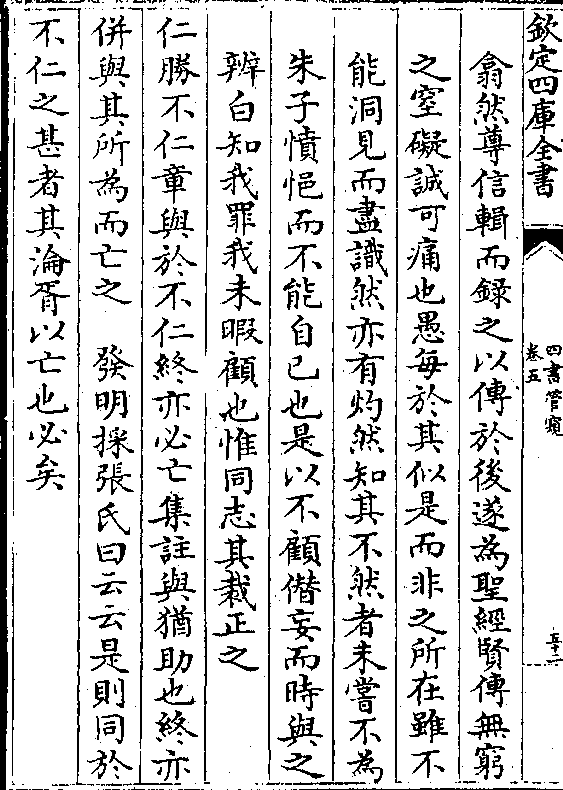 翕然尊信辑而录之以传于后遂为圣经贤传无穷
翕然尊信辑而录之以传于后遂为圣经贤传无穷之窒碍诚可痛也愚每于其似是而非之所在虽不
能洞见而尽识然亦有灼然知其不然者未尝不为
朱子愤悒而不能自已也是以不顾僣妄而时与之
辨白知我罪我未暇顾也惟同志其裁正之
仁胜不仁章与于不仁终亦必亡集注与犹助也终亦
并与其所为而亡之 𤼵明采张氏曰云云是则同于
不仁之甚者其沦胥以亡也必矣
卷五 第 53a 页 WYG0204-0836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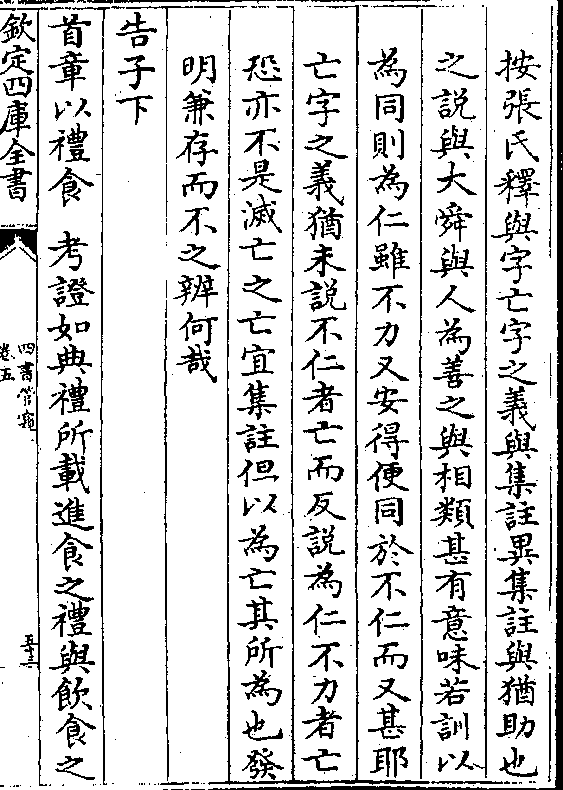 按张氏释与字亡字之义与集注异集注与犹助也
按张氏释与字亡字之义与集注异集注与犹助也之说与大舜与人为善之与相类甚有意味若训以
为同则为仁虽不力又安得便同于不仁而又甚耶
亡字之义犹未说不仁者亡而反说为仁不力者亡
恐亦不是灭亡之亡宜集注但以为亡其所为也𤼵
明兼存而不之辨何哉
告子下
首章以礼食 考證如典礼所载进食之礼与饮食之
卷五 第 53b 页 WYG0204-0836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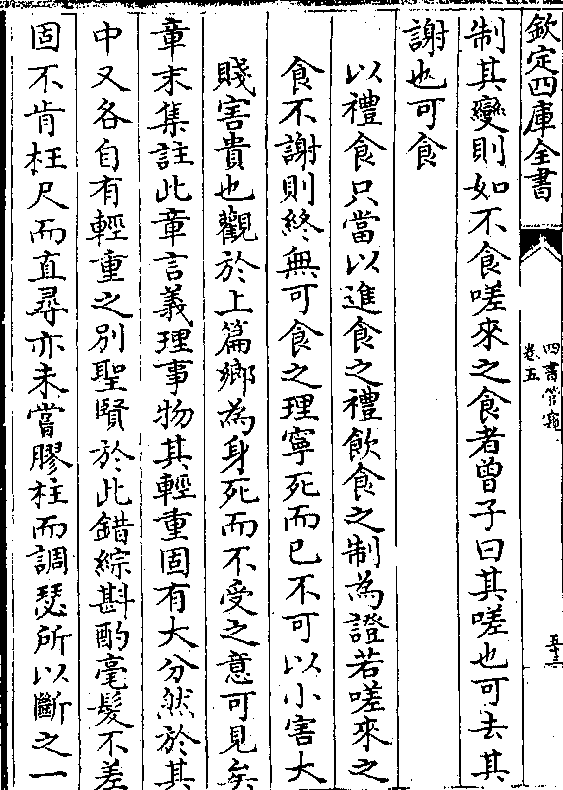 制其变则如不食嗟来之食者曾子曰其嗟也可去其
制其变则如不食嗟来之食者曾子曰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
以礼食只当以进食之礼饮食之制为證若嗟来之
食不谢则终无可食之理宁死而已不可以小害大
贱害贵也观于上篇乡为身死而不受之意可见矣
章末集注此章言义理事物其轻重固有大分然于其
中又各自有轻重之别圣贤于此错综斟酌毫发不差
固不肯枉尺而直寻亦未尝胶柱而调瑟所以断之一
卷五 第 54a 页 WYG0204-0837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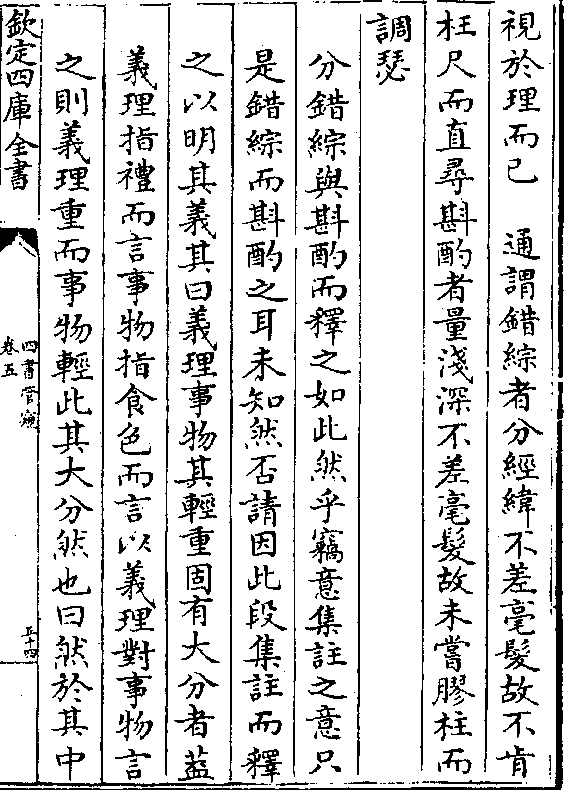 视于理而已 通谓错综者分经纬不差毫发故不肯
视于理而已 通谓错综者分经纬不差毫发故不肯枉尺而直寻斟酌者量浅深不差毫发故未尝胶柱而
调瑟
分错综与斟酌而释之如此然乎窃意集注之意只
是错综而斟酌之耳未知然否请因此段集注而释
之以明其义其曰义理事物其轻重固有大分者盖
义理指礼而言事物指食色而言以义理对事物言
之则义理重而事物轻此其大分然也曰然于其中
卷五 第 54b 页 WYG0204-0837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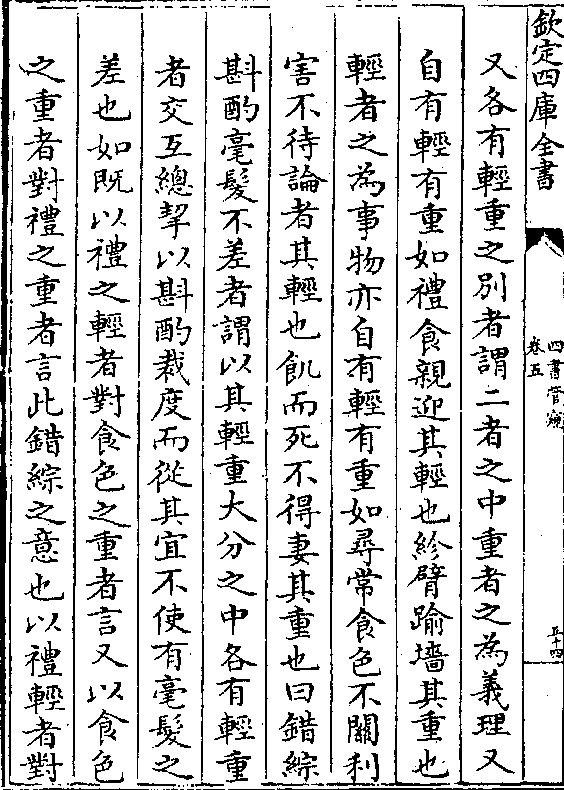 又各有轻重之别者谓二者之中重者之为义理又
又各有轻重之别者谓二者之中重者之为义理又自有轻有重如礼食亲迎其轻也紾臂踰墙其重也
轻者之为事物亦自有轻有重如寻常食色不关利
害不待论者其轻也饥而死不得妻其重也曰错综
斟酌毫发不差者谓以其轻重大分之中各有轻重
者交互总挈以斟酌裁度而从其宜不使有毫发之
差也如既以礼之轻者对食色之重者言又以食色
之重者对礼之重者言此错综之意也以礼轻者对
卷五 第 55a 页 WYG0204-0837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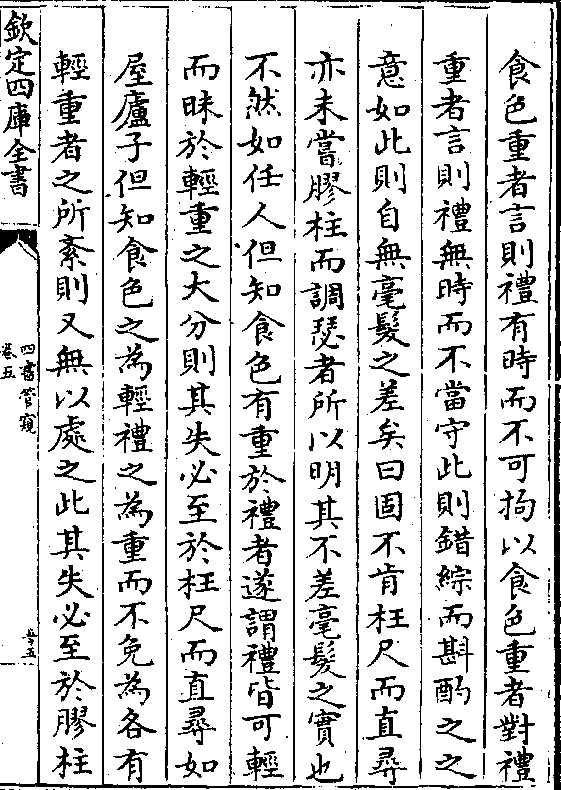 食色重者言则礼有时而不可拘以食色重者对礼
食色重者言则礼有时而不可拘以食色重者对礼重者言则礼无时而不当守此则错综而斟酌之之
意如此则自无毫发之差矣曰固不肯枉尺而直寻
亦未尝胶柱而调瑟者所以明其不差毫发之实也
不然如任人但知食色有重于礼者遂谓礼皆可轻
而昧于轻重之大分则其失必至于枉尺而直寻如
屋庐子但知食色之为轻礼之为重而不免为各有
轻重者之所紊则又无以处之此其失必至于胶柱
卷五 第 55b 页 WYG0204-0837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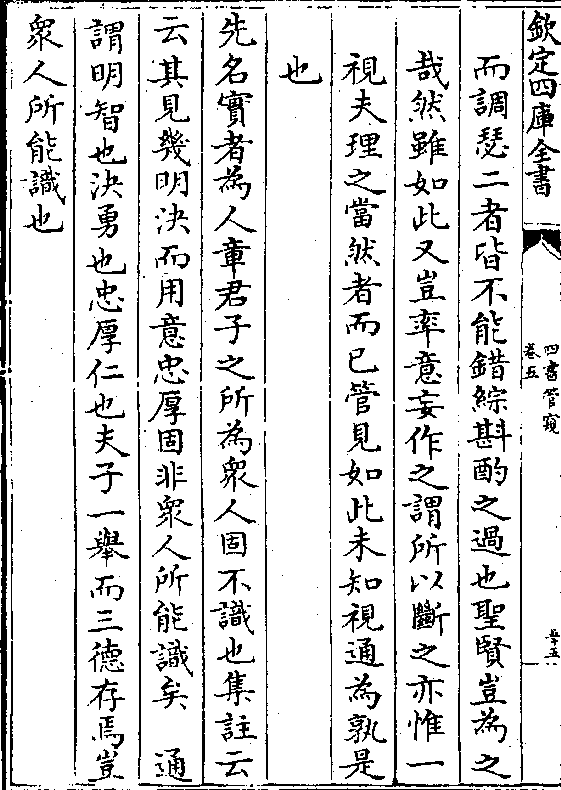 而调瑟二者皆不能错综斟酌之过也圣贤岂为之
而调瑟二者皆不能错综斟酌之过也圣贤岂为之哉然虽如此又岂率意妄作之谓所以断之亦惟一
视夫理之当然者而已管见如此未知视通为孰是
也
先名实者为人章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集注云
云其见几明决而用意忠厚固非众人所能识矣 通
谓明智也决勇也忠厚仁也夫子一举而三德存焉岂
众人所能识也
卷五 第 56a 页 WYG0204-0838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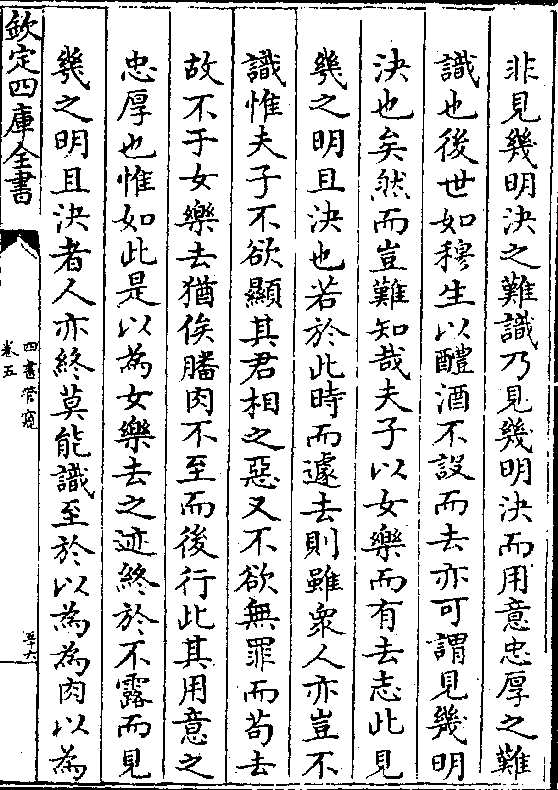 非见几明决之难识乃见几明决而用意忠厚之难
非见几明决之难识乃见几明决而用意忠厚之难识也后世如穆生以醴酒不设而去亦可谓见几明
决也矣然而岂难知哉夫子以女乐而有去志此见
几之明且决也若于此时而遽去则虽众人亦岂不
识惟夫子不欲显其君相之恶又不欲无罪而苟去
故不于女乐去犹俟膰肉不至而后行此其用意之
忠厚也惟如此是以为女乐去之迹终于不露而见
几之明且决者人亦终莫能识至于以为为肉以为
卷五 第 56b 页 WYG0204-0838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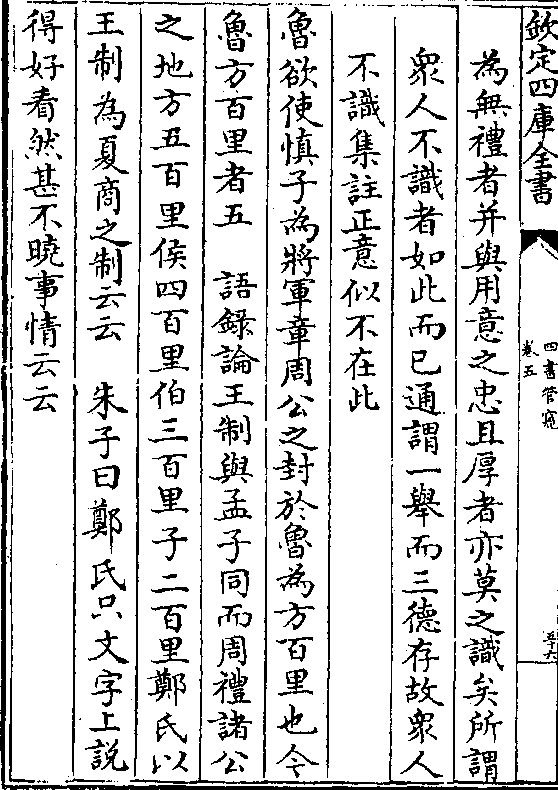 为无礼者并与用意之忠且厚者亦莫之识矣所谓
为无礼者并与用意之忠且厚者亦莫之识矣所谓众人不识者如此而已通谓一举而三德存故众人
不识集注正意似不在此
鲁欲使慎子为将军章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今
鲁方百里者五 语录论王制与孟子同而周礼诸公
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郑氏以
王制为夏商之制云云 朱子曰郑氏只文字上说
得好看然甚不晓事情云云
卷五 第 57a 页 WYG0204-0838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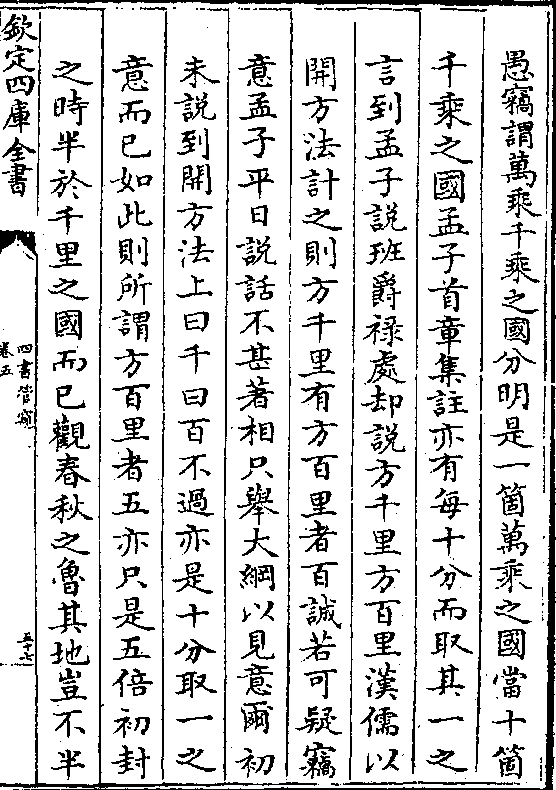 愚窃谓万乘千乘之国分明是一个万乘之国当十个
愚窃谓万乘千乘之国分明是一个万乘之国当十个千乘之国孟子首章集注亦有每十分而取其一之
言到孟子说班爵禄处却说方千里方百里汉儒以
开方法计之则方千里有方百里者百诚若可疑窃
意孟子平日说话不甚著相只举大纲以见意尔初
未说到开方法上曰千曰百不过亦是十分取一之
意而已如此则所谓方百里者五亦只是五倍初封
之时半于千里之国而已观春秋之鲁其地岂不半
卷五 第 57b 页 WYG0204-0838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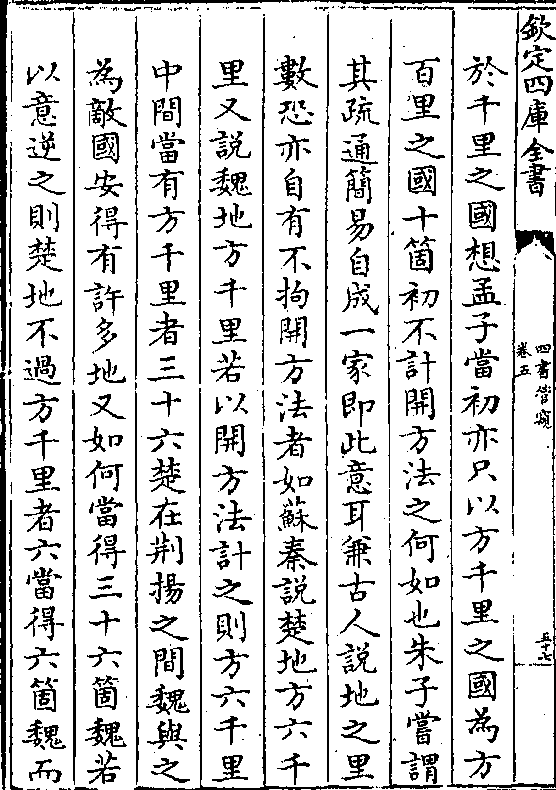 于千里之国想孟子当初亦只以方千里之国为方
于千里之国想孟子当初亦只以方千里之国为方百里之国十个初不计开方法之何如也朱子尝谓
其疏通简易自成一家即此意耳兼古人说地之里
数恐亦自有不拘开方法者如苏秦说楚地方六千
里又说魏地方千里若以开方法计之则方六千里
中间当有方千里者三十六楚在荆扬之间魏与之
为敌国安得有许多地又如何当得三十六个魏若
以意逆之则楚地不过方千里者六当得六个魏而
卷五 第 58a 页 WYG0204-0839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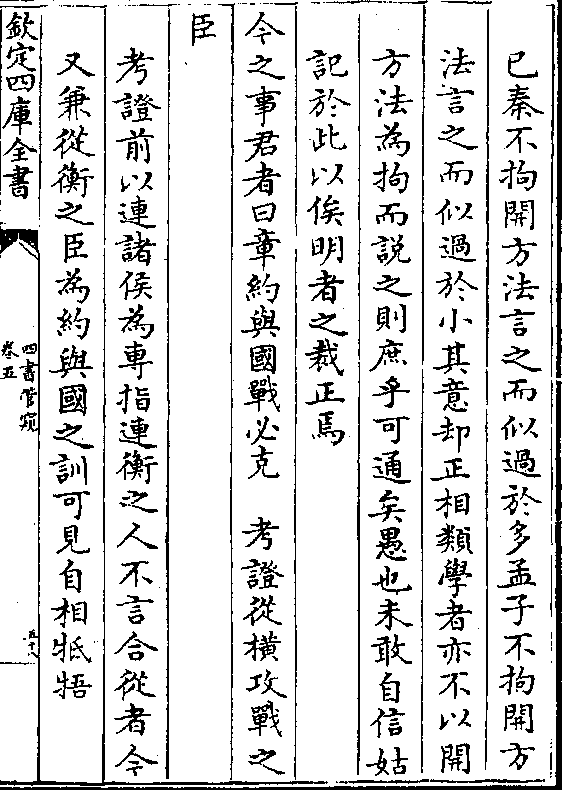 已秦不拘开方法言之而似过于多孟子不拘开方
已秦不拘开方法言之而似过于多孟子不拘开方法言之而似过于小其意却正相类学者亦不以开
方法为拘而说之则庶乎可通矣愚也未敢自信姑
记于此以俟明者之裁正焉
今之事君者曰章约与国战必克 考證从横攻战之
臣
考證前以连诸侯为专指连衡之人不言合从者今
又兼从衡之臣为约与国之训可见自相牴牾
卷五 第 58b 页 WYG0204-0839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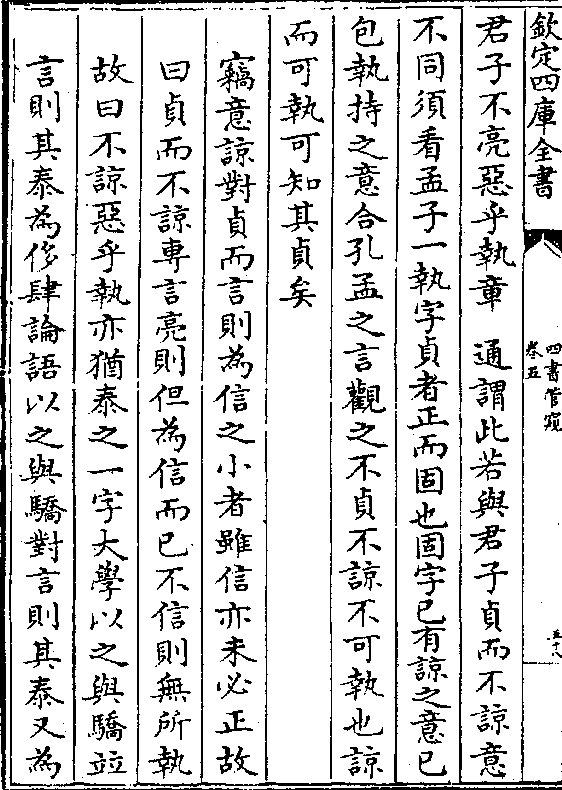 君子不亮恶乎执章 通谓此若与君子贞而不谅意
君子不亮恶乎执章 通谓此若与君子贞而不谅意不同须看孟子一执字贞者正而固也固字已有谅之意已
包执持之意合孔孟之言观之不贞不谅不可执也谅
而可执可知其贞矣
窃意谅对贞而言则为信之小者虽信亦未必正故
曰贞而不谅专言亮则但为信而已不信则无所执
故曰不谅恶乎执亦犹泰之一字大学以之与骄并
言则其泰为侈肆论语以之与骄对言则其泰又为
卷五 第 59a 页 WYG0204-0839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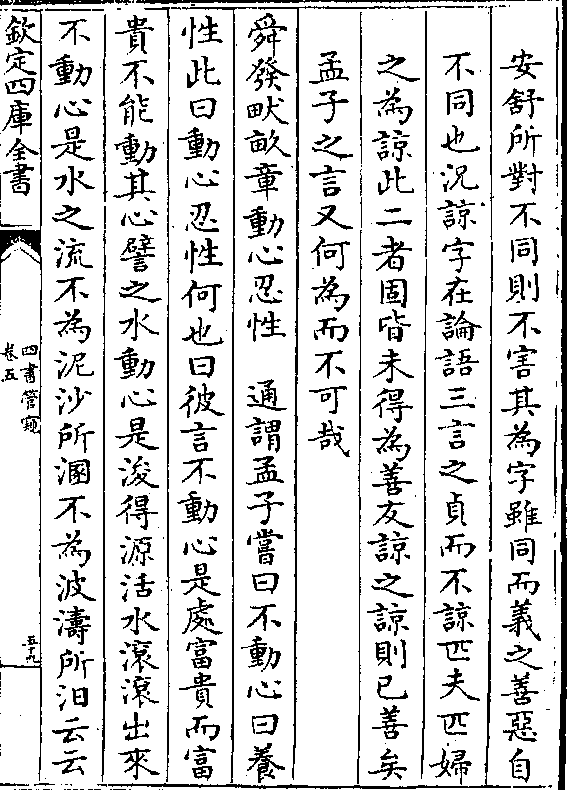 安舒所对不同则不害其为字虽同而义之善恶自
安舒所对不同则不害其为字虽同而义之善恶自不同也况谅字在论语三言之贞而不谅匹夫匹妇
之为谅此二者固皆未得为善友谅之谅则已善矣
孟子之言又何为而不可哉
舜𤼵畎亩章动心忍性 通谓孟子尝曰不动心曰养
性此曰动心忍性何也曰彼言不动心是处富贵而富
贵不能动其心譬之水动心是浚得源活水滚滚出来
不动心是水之流不为泥沙所溷不为波涛所汩云云
卷五 第 59b 页 WYG0204-0839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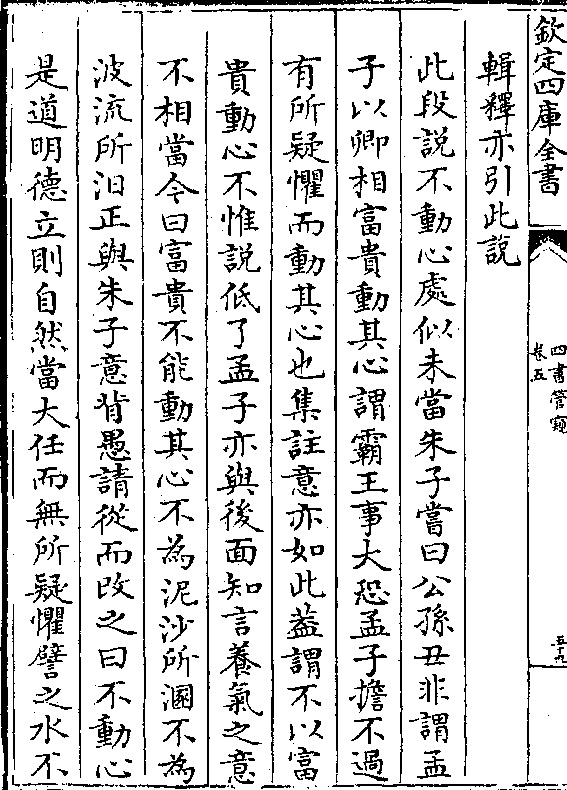 辑释亦引此说
辑释亦引此说此段说不动心处似未当朱子尝曰公孙丑非谓孟
子以卿相富贵动其心谓霸王事大恐孟子担不过
有所疑惧而动其心也集注意亦如此盖谓不以富
贵动心不惟说低了孟子亦与后面知言养气之意
不相当今曰富贵不能动其心不为泥沙所溷不为
波流所汩正与朱子意背愚请从而改之曰不动心
是道明德立则自然当大任而无所疑惧譬之水不
卷五 第 60a 页 WYG0204-0840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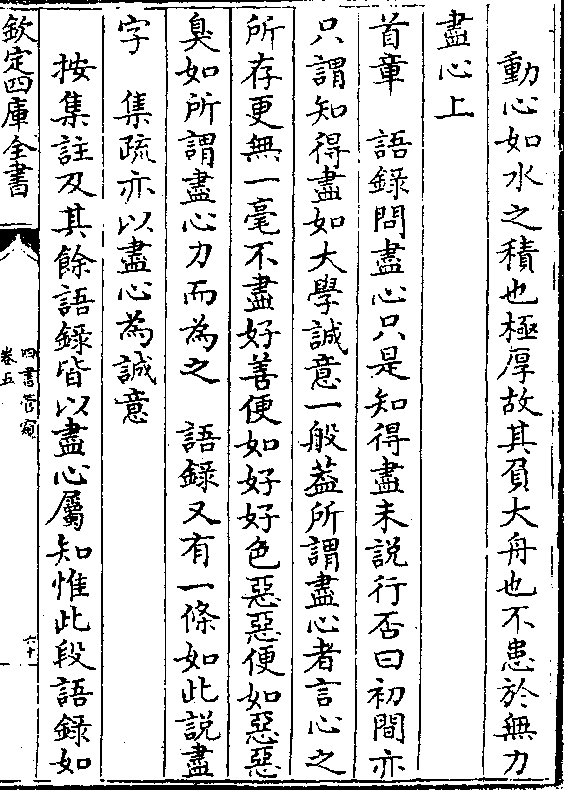 动心如水之积也极厚故其负大舟也不患于无力
动心如水之积也极厚故其负大舟也不患于无力尽心上
首章 语录问尽心只是知得尽未说行否曰初间亦
只谓知得尽如大学诚意一般盖所谓尽心者言心之
所存更无一毫不尽好善便如好好色恶恶便如恶恶
臭如所谓尽心力而为之 语录又有一条如此说尽
字 集疏亦以尽心为诚意
按集注及其馀语录皆以尽心属知惟此段语录如
卷五 第 60b 页 WYG0204-0840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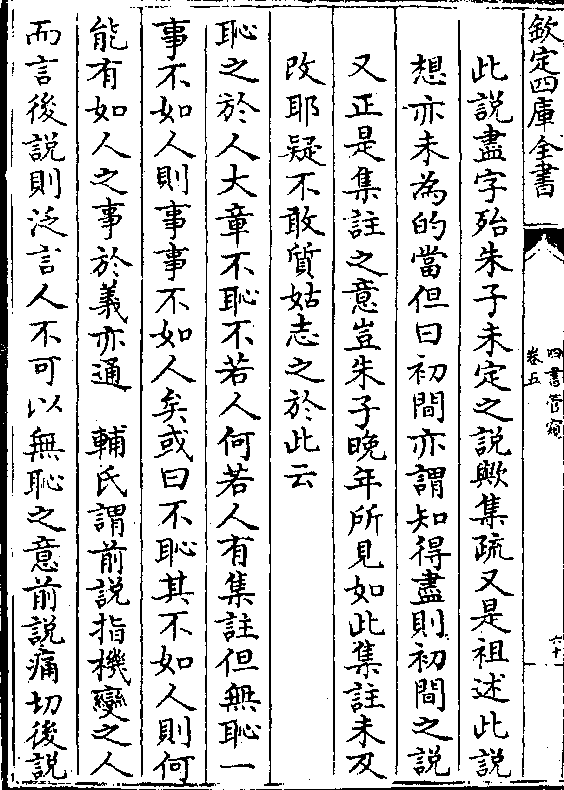 此说尽字殆朱子未定之说欤集疏又是祖述此说
此说尽字殆朱子未定之说欤集疏又是祖述此说想亦未为的当但曰初间亦谓知得尽则初间之说
又正是集注之意岂朱子晚年所见如此集注未及
改耶疑不敢质姑志之于此云
耻之于人大章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集注但无耻一
事不如人则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耻其不如人则何
能有如人之事于义亦通 辅氏谓前说指机变之人
而言后说则泛言人不可以无耻之意前说痛切后说
卷五 第 61a 页 WYG0204-0840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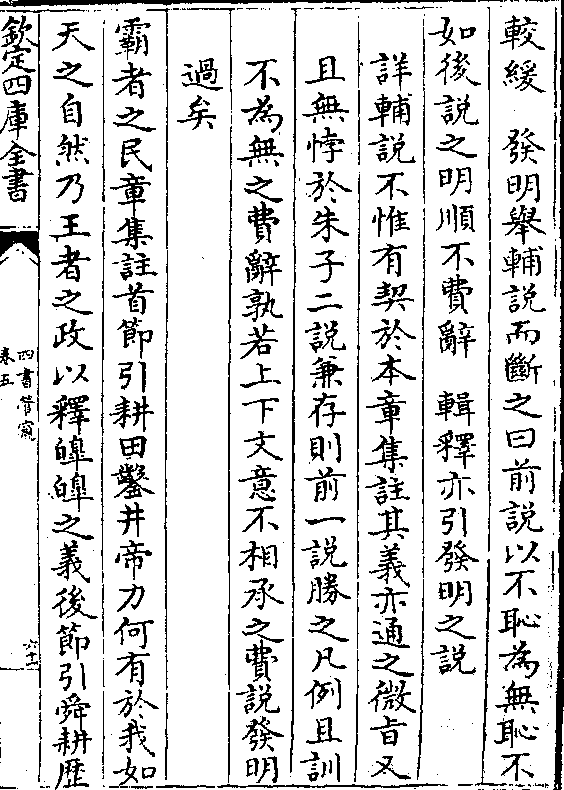 较缓 𤼵明举辅说而断之曰前说以不耻为无耻不
较缓 𤼵明举辅说而断之曰前说以不耻为无耻不如后说之明顺不费辞 辑释亦引𤼵明之说
详辅说不惟有契于本章集注其义亦通之微旨又
且无悖于朱子二说兼存则前一说胜之凡例且训
不为无之费辞孰若上下文意不相承之费说𤼵明
过矣
霸者之民章集注首节引耕田凿井帝力何有于我如
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以释皞皞之义后节引舜耕历
卷五 第 61b 页 WYG0204-0840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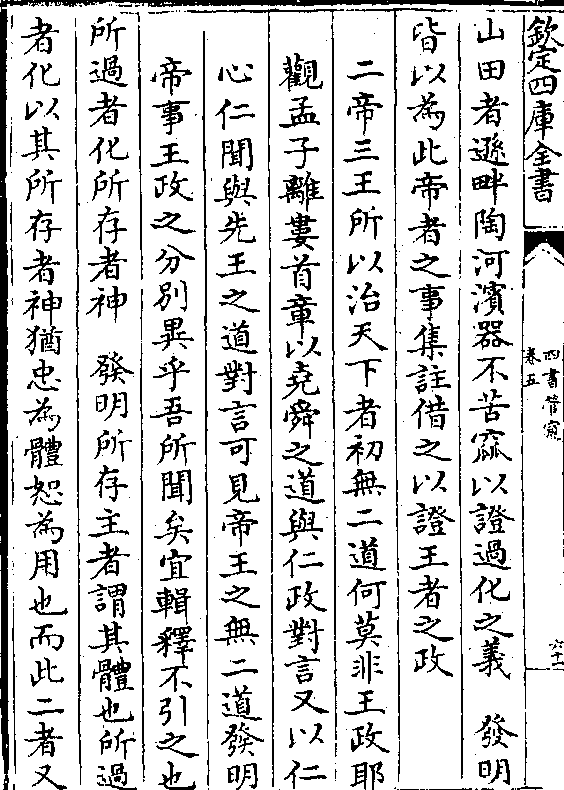 山田者逊畔陶河滨器不苦窳以證过化之义 发明
山田者逊畔陶河滨器不苦窳以證过化之义 发明皆以为此帝者之事集注借之以證王者之政
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者初无二道何莫非王政耶
观孟子离娄首章以尧舜之道与仁政对言又以仁
心仁闻与先王之道对言可见帝王之无二道𤼵明
帝事王政之分别异乎吾所闻矣宜辑释不引之也
所过者化所存者神 𤼵明所存主者谓其体也所过
者化以其所存者神犹忠为体恕为用也而此二者又
卷五 第 62a 页 WYG0204-0841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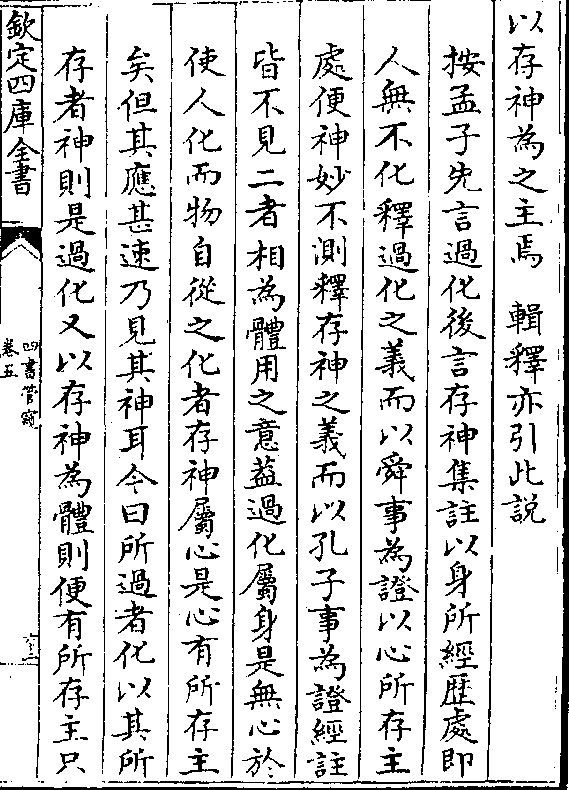 以存神为之主焉 辑释亦引此说
以存神为之主焉 辑释亦引此说按孟子先言过化后言存神集注以身所经历处即
人无不化释过化之义而以舜事为證以心所存主
处便神妙不测释存神之义而以孔子事为證经注
皆不见二者相为体用之意盖过化属身是无心于
使人化而物自从之化者存神属心是心有所存主
矣但其应甚速乃见其神耳今曰所过者化以其所
存者神则是过化又以存神为体则便有所存主只
卷五 第 62b 页 WYG0204-0841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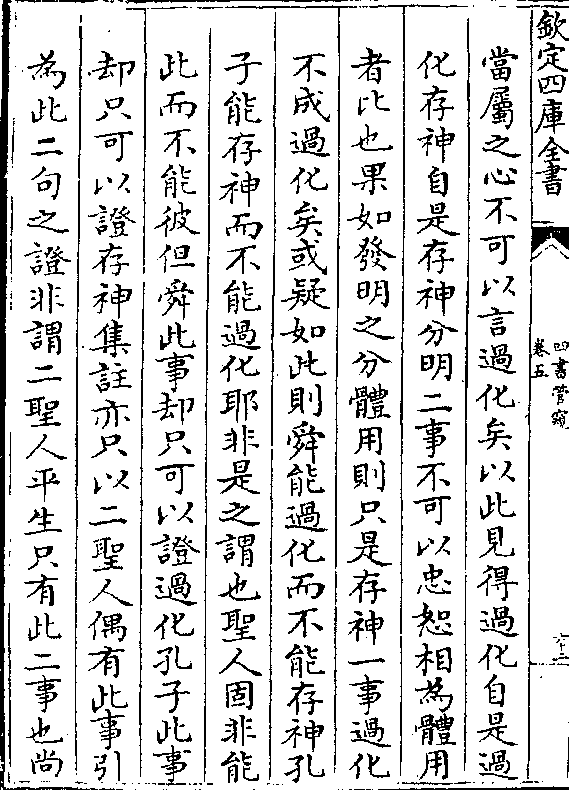 当属之心不可以言过化矣以此见得过化自是过
当属之心不可以言过化矣以此见得过化自是过化存神自是存神分明二事不可以忠恕相为体用
者比也果如发明之分体用则只是存神一事过化
不成过化矣或疑如此则舜能过化而不能存神孔
子能存神而不能过化耶非是之谓也圣人固非能
此而不能彼但舜此事却只可以證过化孔子此事
却只可以證存神集注亦只以二圣人偶有此事引
为此二句之證非谓二圣人平生只有此二事也尚
卷五 第 63a 页 WYG0204-0841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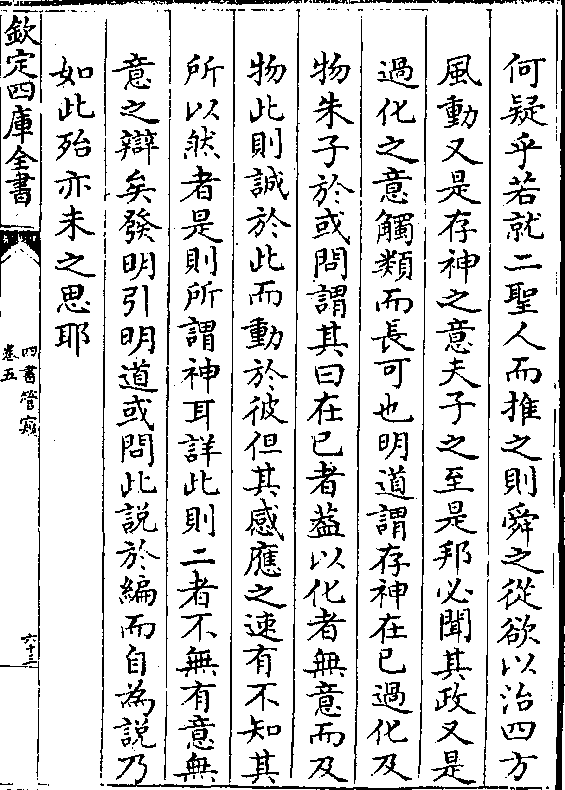 何疑乎若就二圣人而推之则舜之从欲以治四方
何疑乎若就二圣人而推之则舜之从欲以治四方风动又是存神之意夫子之至是邦必闻其政又是
过化之意触类而长可也明道谓存神在己过化及
物朱子于或问谓其曰在己者盖以化者无意而及
物此则诚于此而动于彼但其感应之速有不知其
所以然者是则所谓神耳详此则二者不无有意无
意之辩矣𤼵明引明道或问此说于编而自为说乃
如此殆亦未之思耶
卷五 第 63b 页 WYG0204-0841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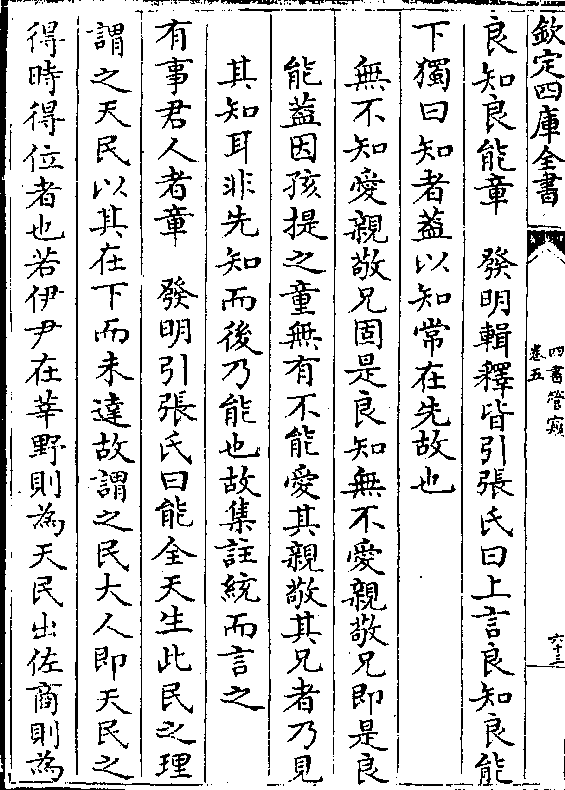 良知良能章 𤼵明辑释皆引张氏曰上言良知良能
良知良能章 𤼵明辑释皆引张氏曰上言良知良能下独曰知者盖以知常在先故也
无不知爱亲敬兄固是良知无不爱亲敬兄即是良
能盖因孩提之童无有不能爱其亲敬其兄者乃见
其知耳非先知而后乃能也故集注统而言之
有事君人者章 𤼵明引张氏曰能全天生此民之理
谓之天民以其在下而未达故谓之民大人即天民之
得时得位者也若伊尹在莘野则为天民出佐商则为
卷五 第 64a 页 WYG0204-0842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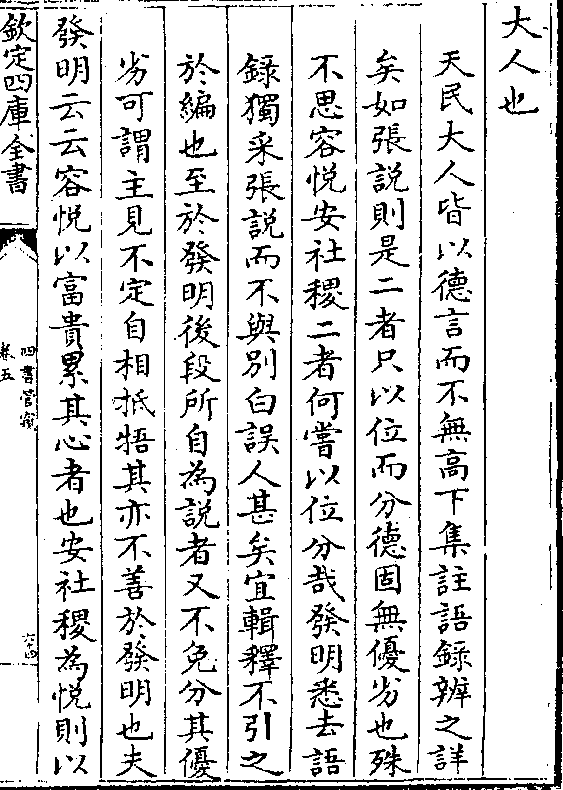 大人也
大人也天民大人皆以德言而不无高下集注语录辨之详
矣如张说则是二者只以位而分德固无优劣也殊
不思容悦安社稷二者何尝以位分哉𤼵明悉去语
录独采张说而不与别白误人甚矣宜辑释不引之
于编也至于𤼵明后段所自为说者又不免分其优
劣可谓主见不定自相抵牾其亦不善于𤼵明也夫
𤼵明云云容悦以富贵累其心者也安社稷为悦则以
卷五 第 64b 页 WYG0204-0842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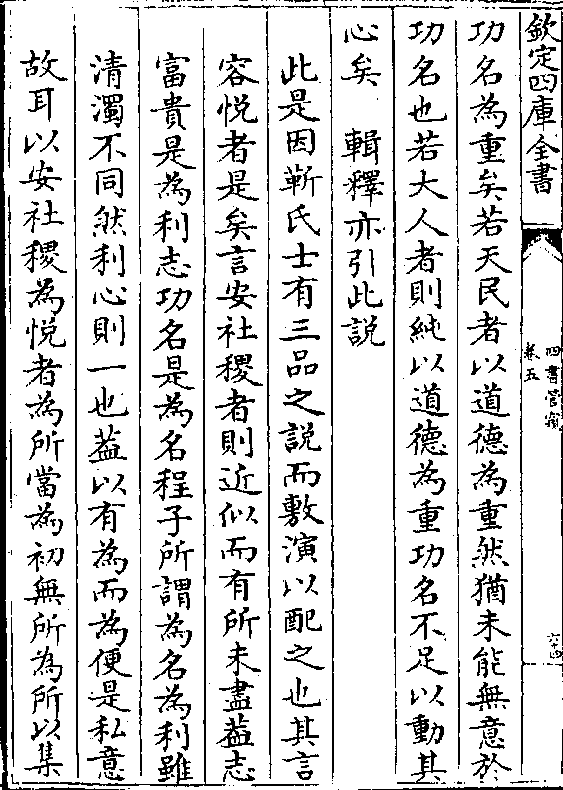 功名为重矣若天民者以道德为重然犹未能无意于
功名为重矣若天民者以道德为重然犹未能无意于功名也若大人者则纯以道德为重功名不足以动其
心矣 辑释亦引此说
此是因靳氏士有三品之说而敷演以配之也其言
容悦者是矣言安社稷者则近似而有所未尽盖志
富贵是为利志功名是为名程子所谓为名为利虽
清浊不同然利心则一也盖以有为而为便是私意
故耳以安社稷为悦者为所当为初无所为所以集
卷五 第 65a 页 WYG0204-0842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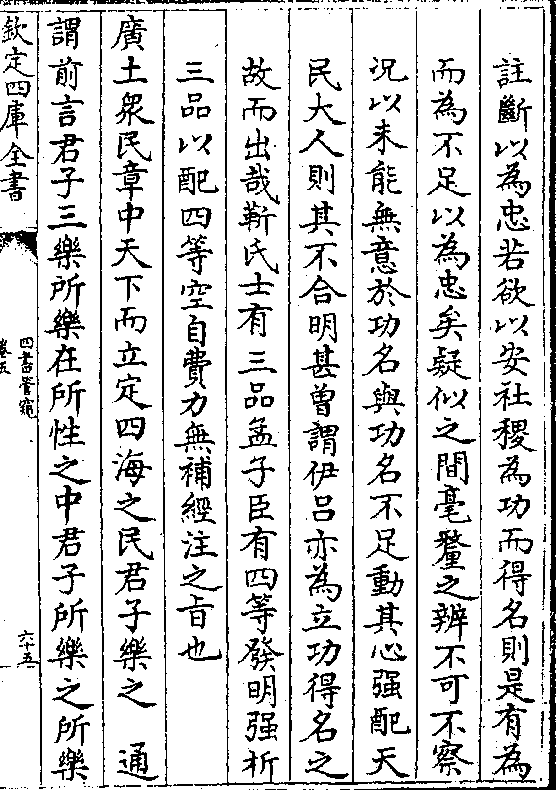 注断以为忠若欲以安社稷为功而得名则是有为
注断以为忠若欲以安社稷为功而得名则是有为而为不足以为忠矣疑似之间毫釐之辨不可不察
况以未能无意于功名与功名不足动其心强配天
民大人则其不合明甚曾谓伊吕亦为立功得名之
故而出哉靳氏士有三品孟子臣有四等𤼵明强析
三品以配四等空自费力无补经注之旨也
广土众民章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 通
谓前言君子三乐所乐在所性之中君子所乐之所乐
卷五 第 65b 页 WYG0204-0842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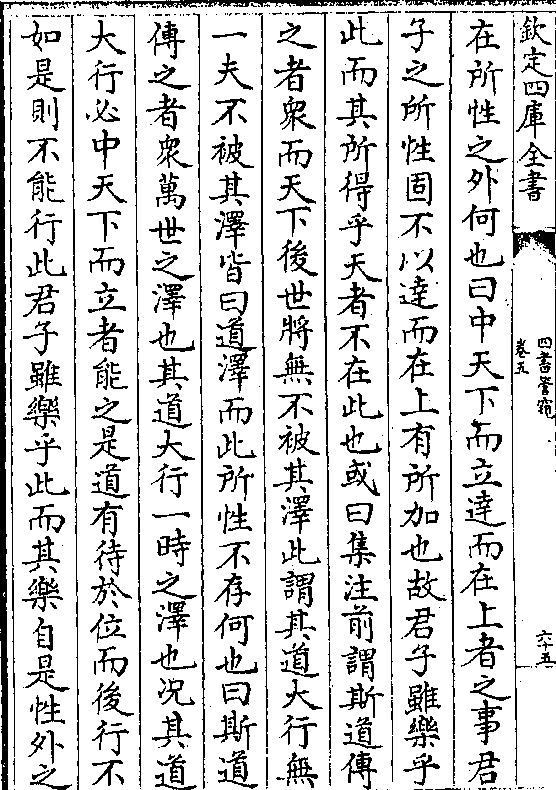 在所性之外何也曰中天下而立达而在上者之事君
在所性之外何也曰中天下而立达而在上者之事君子之所性固不以达而在上有所加也故君子虽乐乎
此而其所得乎天者不在此也或曰集注前谓斯道传
之者众而天下后世将无不被其泽此谓其道大行无
一夫不被其泽皆曰道泽而此所性不存何也曰斯道
传之者众万世之泽也其道大行一时之泽也况其道
大行必中天下而立者能之是道有待于位而后行不
如是则不能行此君子虽乐乎此而其乐自是性外之
卷五 第 66a 页 WYG0204-0843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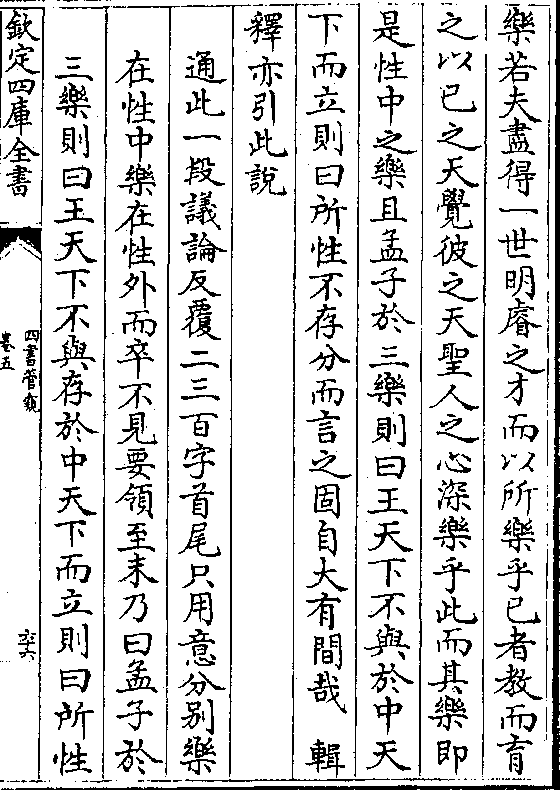 乐若夫尽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乐乎己者教而育
乐若夫尽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乐乎己者教而育之以己之天觉彼之天圣人之心深乐乎此而其乐即
是性中之乐且孟子于三乐则曰王天下不与于中天
下而立则曰所性不存分而言之固自大有间哉 辑
释亦引此说
通此一段议论反覆二三百字首尾只用意分别乐
在性中乐在性外而卒不见要领至末乃曰孟子于
三乐则曰王天下不与存于中天下而立则曰所性
卷五 第 66b 页 WYG0204-0843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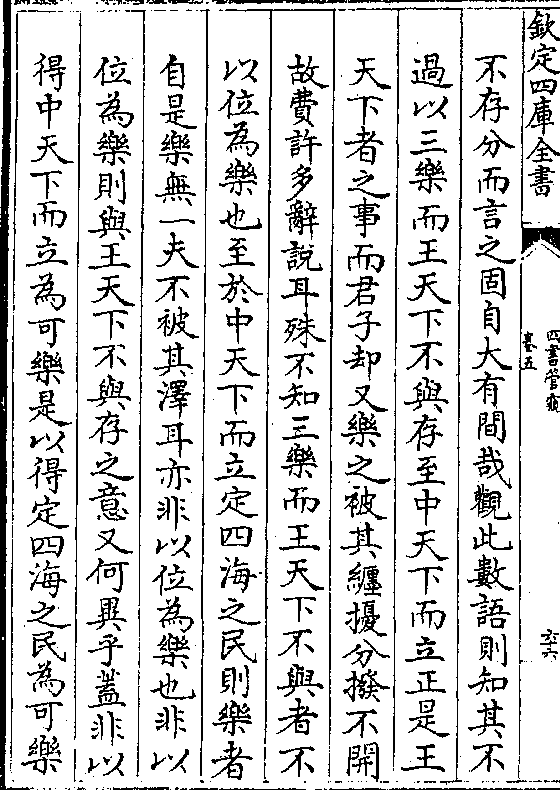 不存分而言之固自大有间哉观此数语则知其不
不存分而言之固自大有间哉观此数语则知其不过以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至中天下而立正是王
天下者之事而君子却又乐之被其缠扰分拨不开
故费许多辞说耳殊不知三乐而王天下不与者不
以位为乐也至于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则乐者
自是乐无一夫不被其泽耳亦非以位为乐也非以
位为乐则与王天下不与存之意又何异乎盖非以
得中天下而立为可乐是以得定四海之民为可乐
卷五 第 67a 页 WYG0204-0843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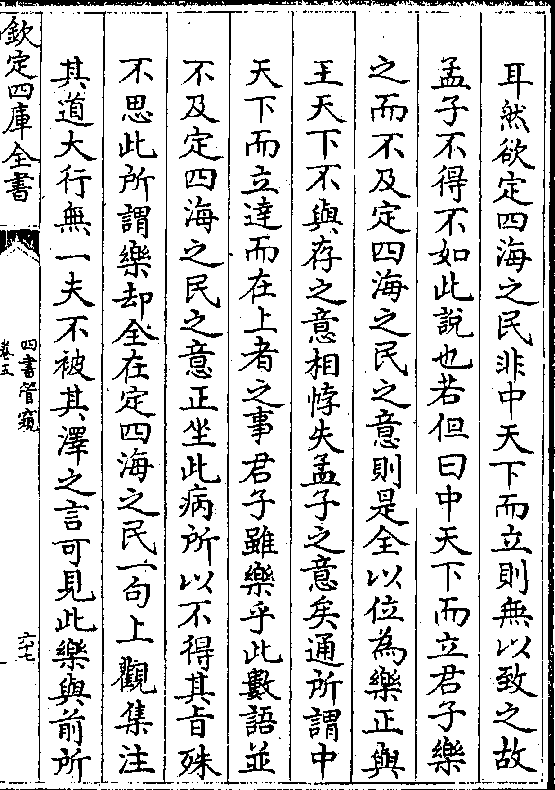 耳然欲定四海之民非中天下而立则无以致之故
耳然欲定四海之民非中天下而立则无以致之故孟子不得不如此说也若但曰中天下而立君子乐
之而不及定四海之民之意则是全以位为乐正与
王天下不与存之意相悖失孟子之意矣通所谓中
天下而立达而在上者之事君子虽乐乎此数语并
不及定四海之民之意正坐此病所以不得其旨殊
不思此所谓乐却全在定四海之民一句上观集注
其道大行无一夫不被其泽之言可见此乐与前所
卷五 第 67b 页 WYG0204-0843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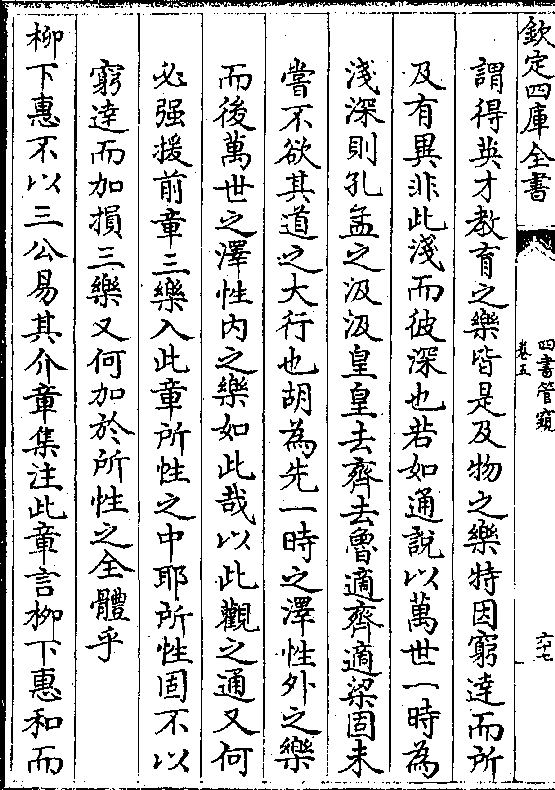 谓得英才教育之乐皆是及物之乐特因穷达而所
谓得英才教育之乐皆是及物之乐特因穷达而所及有异非此浅而彼深也若如通说以万世一时为
浅深则孔孟之汲汲皇皇去齐去鲁适齐适梁固未
尝不欲其道之大行也胡为先一时之泽性外之乐
而后万世之泽性内之乐如此哉以此观之通又何
必强援前章三乐入此章所性之中耶所性固不以
穷达而加损三乐又何加于所性之全体乎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集注此章言柳下惠和而
卷五 第 68a 页 WYG0204-0844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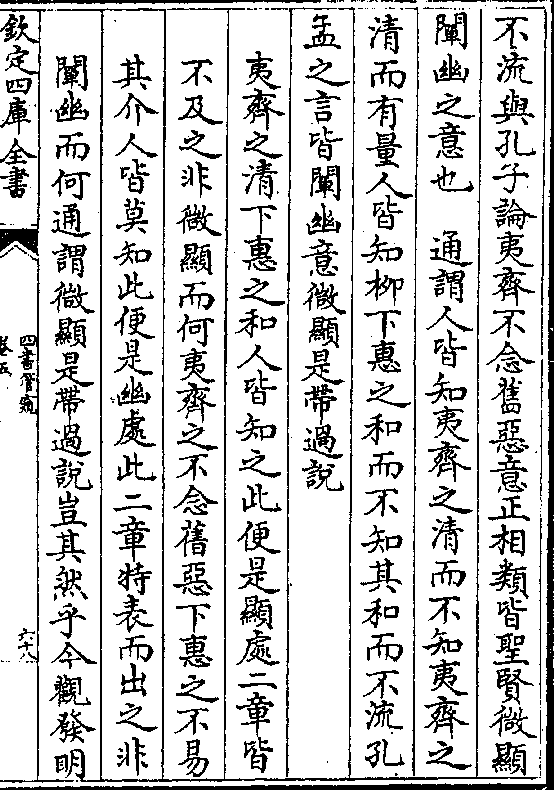 不流与孔子论夷齐不念旧恶意正相类皆圣贤微显
不流与孔子论夷齐不念旧恶意正相类皆圣贤微显阐幽之意也 通谓人皆知夷齐之清而不知夷齐之
清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其和而不流孔
孟之言皆阐幽意微显是带过说
夷齐之清下惠之和人皆知之此便是显处二章皆
不及之非微显而何夷齐之不念旧恶下惠之不易
其介人皆莫知此便是幽处此二章特表而出之非
阐幽而何通谓微显是带过说岂其然乎今观𤼵明
卷五 第 68b 页 WYG0204-0844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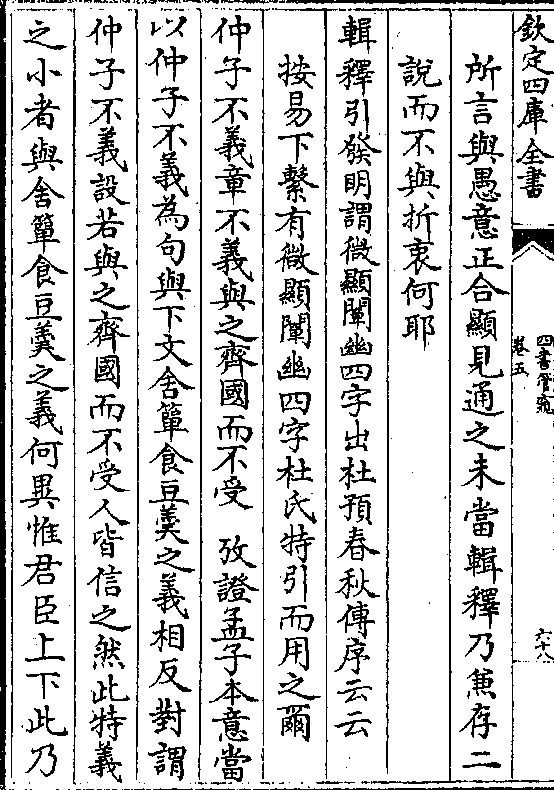 所言与愚意正合显见通之未当辑释乃兼存二
所言与愚意正合显见通之未当辑释乃兼存二说而不与折衷何耶
辑释引𤼵明谓微显阐幽四字出杜预春秋传序云云
按易下系有微显阐幽四字杜氏特引而用之尔
仲子不义章不义与之齐国而不受 考證孟子本意当
以仲子不义为句与下文舍箪食豆羹之义相反对谓
仲子不义设若与之齐国而不受人皆信之然此特义
之小者与舍箪食豆羹之义何异惟君臣上下此乃
卷五 第 69a 页 WYG0204-0844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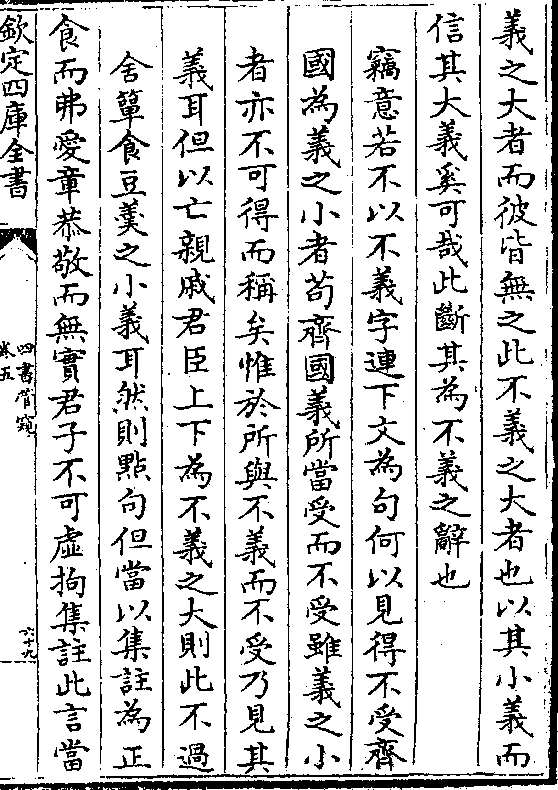 义之大者而彼皆无之此不义之大者也以其小义而
义之大者而彼皆无之此不义之大者也以其小义而信其大义奚可哉此断其为不义之辞也
窃意若不以不义字连下文为句何以见得不受齐
国为义之小者苟齐国义所当受而不受虽义之小
者亦不可得而称矣惟于所与不义而不受乃见其
义耳但以亡亲戚君臣上下为不义之大则此不过
舍箪食豆羹之小义耳然则点句但当以集注为正
食而弗爱章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集注此言当
卷五 第 69b 页 WYG0204-0844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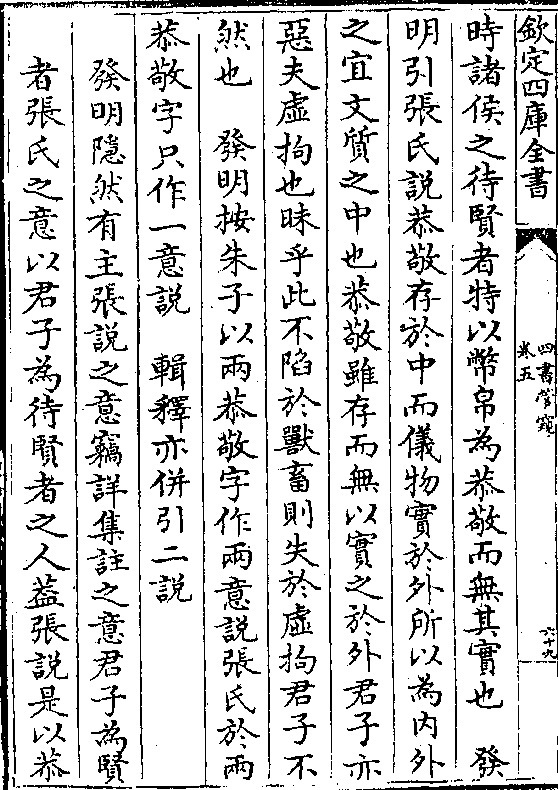 时诸侯之待贤者特以币帛为恭敬而无其实也 𤼵
时诸侯之待贤者特以币帛为恭敬而无其实也 𤼵明引张氏说恭敬存于中而仪物实于外所以为内外
之宜文质之中也恭敬虽存而无以实之于外君子亦
恶夫虚拘也昧乎此不陷于兽畜则失于虚拘君子不
然也 𤼵明按朱子以两恭敬字作两意说张氏于两
恭敬字只作一意说 辑释亦并引二说
𤼵明隐然有主张说之意窃详集注之意君子为贤
者张氏之意以君子为待贤者之人盖张说是以恭
卷五 第 70a 页 WYG0204-0845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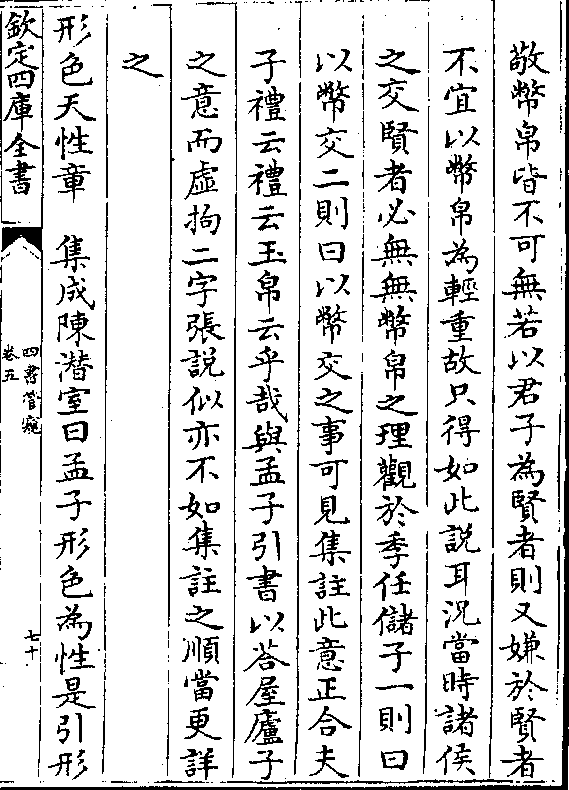 敬币帛皆不可无若以君子为贤者则又嫌于贤者
敬币帛皆不可无若以君子为贤者则又嫌于贤者不宜以币帛为轻重故只得如此说耳况当时诸侯
之交贤者必无无币帛之理观于季任储子一则曰
以币交二则曰以币交之事可见集注此意正合夫
子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与孟子引书以荅屋庐子
之意而虚拘二字张说似亦不如集注之顺当更详
之
形色天性章 集成陈潜室曰孟子形色为性是引形
卷五 第 70b 页 WYG0204-0845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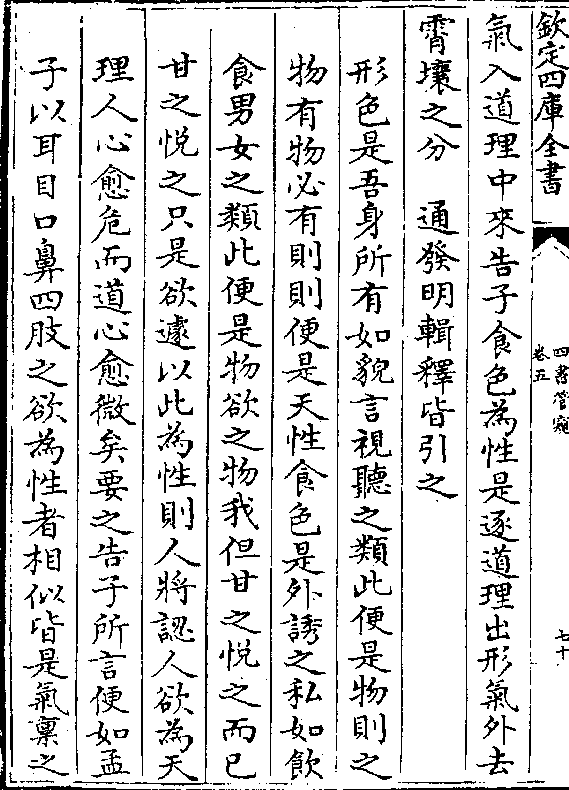 气入道理中来告子食色为性是逐道理出形气外去
气入道理中来告子食色为性是逐道理出形气外去霄壤之分 通𤼵明辑释皆引之
形色是吾身所有如貌言视听之类此便是物则之
物有物必有则则便是天性食色是外诱之私如饮
食男女之类此便是物欲之物我但甘之悦之而已
甘之悦之只是欲遽以此为性则人将认人欲为天
理人心愈危而道心愈微矣要之告子所言便如孟
子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为性者相似皆是气禀之
卷五 第 71a 页 WYG0204-0845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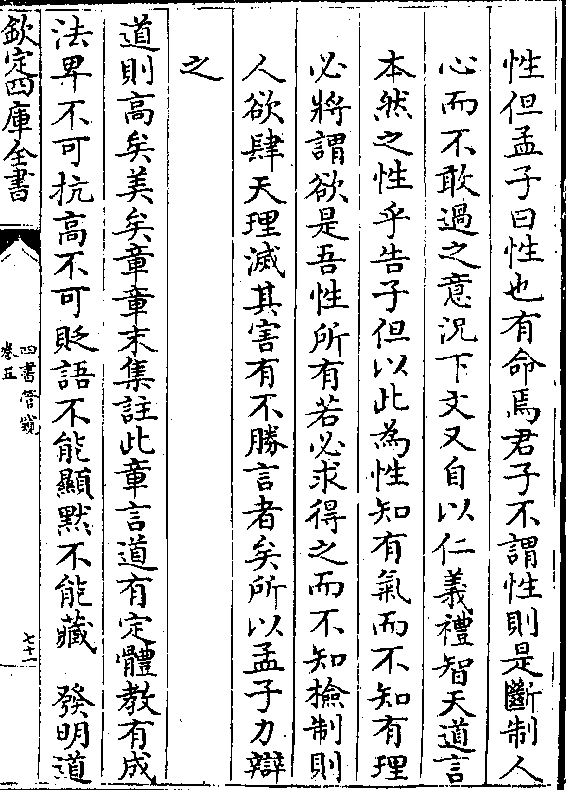 性但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则是断制人
性但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则是断制人心而不敢过之意况下文又自以仁义礼智天道言
本然之性乎告子但以此为性知有气而不知有理
必将谓欲是吾性所有若必求得之而不知检制则
人欲肆天理灭其害有不胜言者矣所以孟子力辩
之
道则高矣美矣章章末集注此章言道有定体教有成
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贬语不能显默不能藏 𤼵明道
卷五 第 71b 页 WYG0204-0845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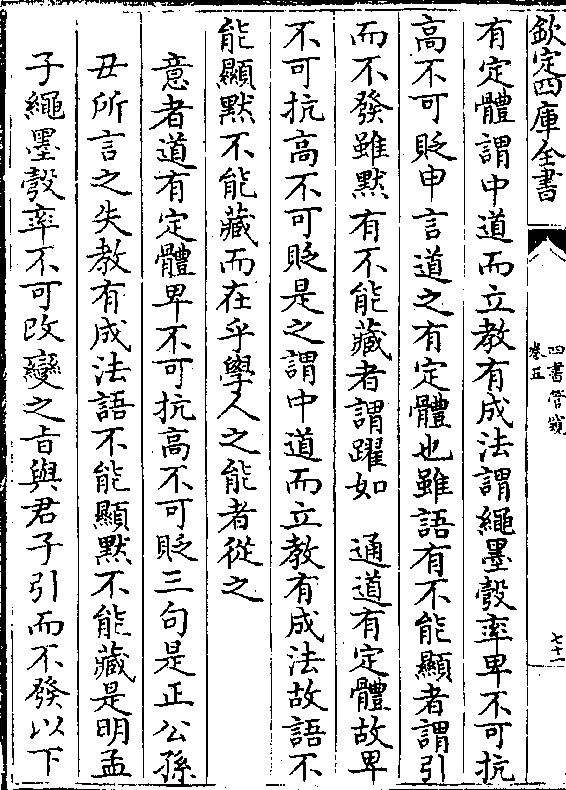 有定体谓中道而立教有成法谓绳墨彀率卑不可抗
有定体谓中道而立教有成法谓绳墨彀率卑不可抗高不可贬申言道之有定体也虽语有不能显者谓引
而不𤼵虽默有不能藏者谓跃如 通道有定体故卑
不可抗高不可贬是之谓中道而立教有成法故语不
能显默不能藏而在乎学人之能者从之
意者道有定体卑不可抗高不可贬三句是正公孙
丑所言之失教有成法语不能显默不能藏是明孟
子绳墨彀率不可改变之旨与君子引而不𤼵以下
卷五 第 72a 页 WYG0204-0846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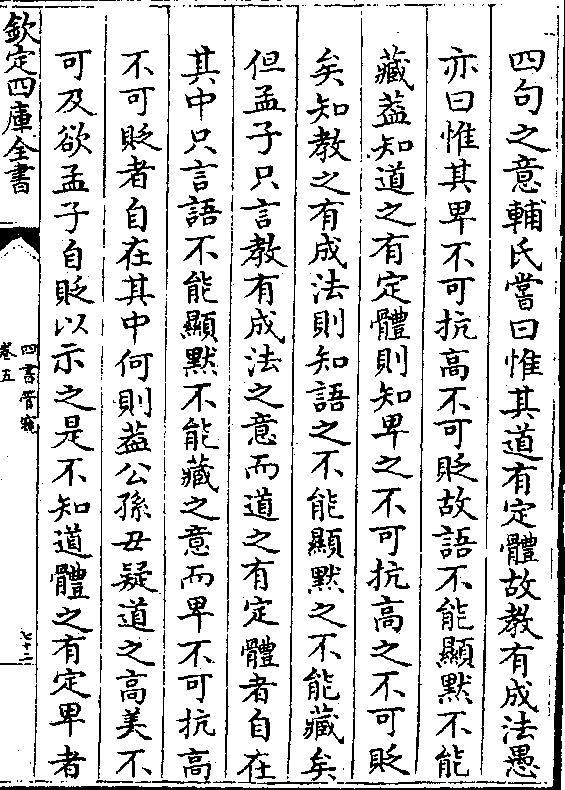 四句之意辅氏尝曰惟其道有定体故教有成法愚
四句之意辅氏尝曰惟其道有定体故教有成法愚亦曰惟其卑不可抗高不可贬故语不能显默不能
藏盖知道之有定体则知卑之不可抗高之不可贬
矣知教之有成法则知语之不能显默之不能藏矣
但孟子只言教有成法之意而道之有定体者自在
其中只言语不能显默不能藏之意而卑不可抗高
不可贬者自在其中何则盖公孙丑疑道之高美不
可及欲孟子自贬以示之是不知道体之有定卑者
卷五 第 72b 页 WYG0204-0846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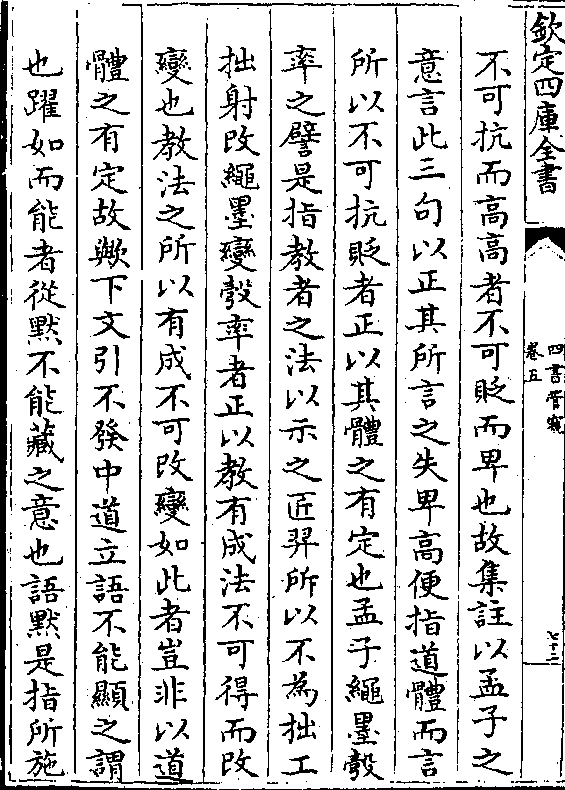 不可抗而高高者不可贬而卑也故集注以孟子之
不可抗而高高者不可贬而卑也故集注以孟子之意言此三句以正其所言之失卑高便指道体而言
所以不可抗贬者正以其体之有定也孟子绳墨彀
率之譬是指教者之法以示之匠羿所以不为拙工
拙射改绳墨变彀率者正以教有成法不可得而改
变也教法之所以有成不可改变如此者岂非以道
体之有定故欤下文引不𤼵中道立语不能显之谓
也跃如而能者从默不能藏之意也语默是指所施
卷五 第 73a 页 WYG0204-0846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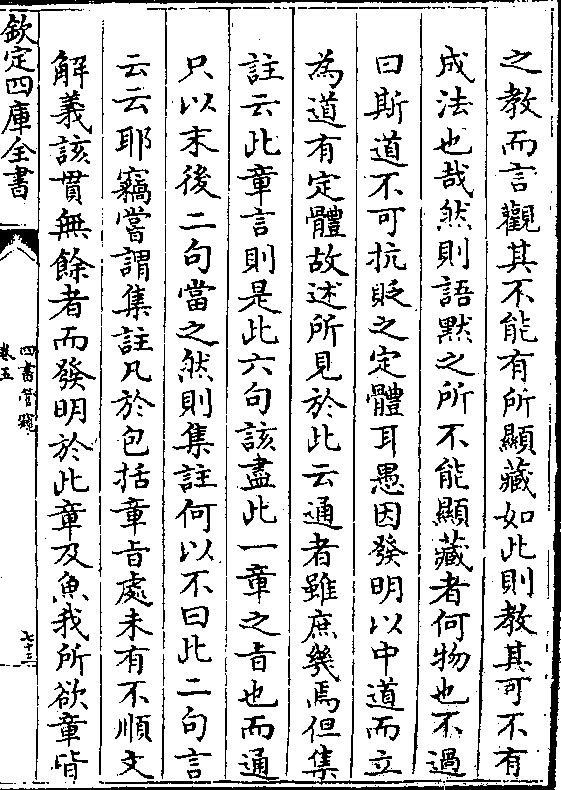 之教而言观其不能有所显藏如此则教其可不有
之教而言观其不能有所显藏如此则教其可不有成法也哉然则语默之所不能显藏者何物也不过
曰斯道不可抗贬之定体耳愚因𤼵明以中道而立
为道有定体故述所见于此云通者虽庶几焉但集
注云此章言则是此六句该尽此一章之旨也而通
只以末后二句当之然则集注何以不曰此二句言
云云耶窃尝谓集注凡于包括章旨处未有不顺文
解义该贯无馀者而𤼵明于此章及鱼我所欲章皆
卷五 第 73b 页 WYG0204-0846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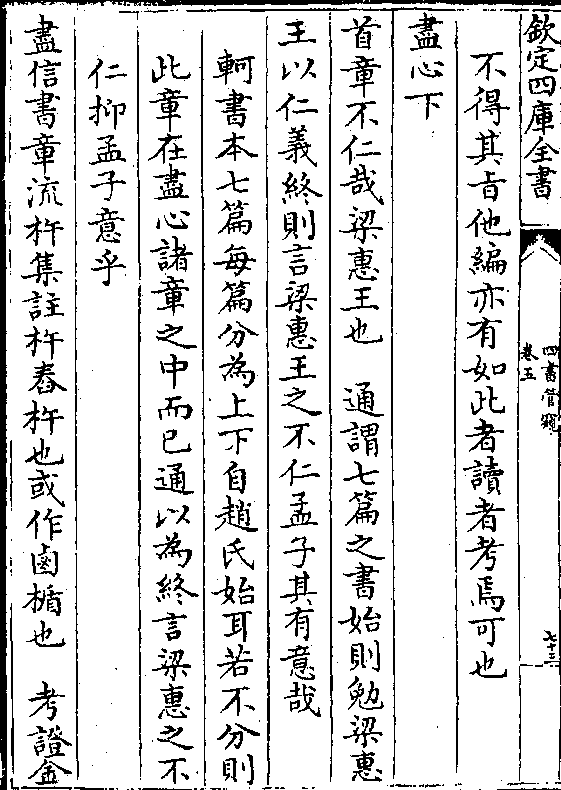 不得其旨他编亦有如此者读者考焉可也
不得其旨他编亦有如此者读者考焉可也尽心下
首章不仁哉梁惠王也 通谓七篇之书始则勉梁惠
王以仁义终则言梁惠王之不仁孟子其有意哉
轲书本七篇每篇分为上下自赵氏始耳若不分则
此章在尽心诸章之中而已通以为终言梁惠之不
仁抑孟子意乎
尽信书章流杵集注杵舂杵也或作卤楯也 考證金
卷五 第 74a 页 WYG0204-0847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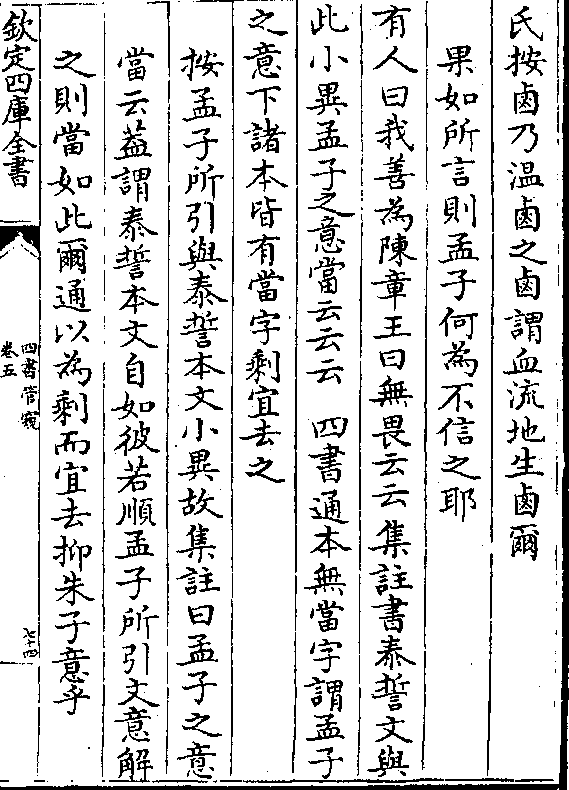 氏按卤乃温卤之卤谓血流地生卤尔
氏按卤乃温卤之卤谓血流地生卤尔果如所言则孟子何为不信之耶
有人曰我善为陈章王曰无畏云云集注书泰誓文与
此小异孟子之意当云云云 四书通本无当字谓孟子
之意下诸本皆有当字剩宜去之
按孟子所引与泰誓本文小异故集注曰孟子之意
当云盖谓泰誓本文自如彼若顺孟子所引文意解
之则当如此尔通以为剩而宜去抑朱子意乎
卷五 第 74b 页 WYG0204-0847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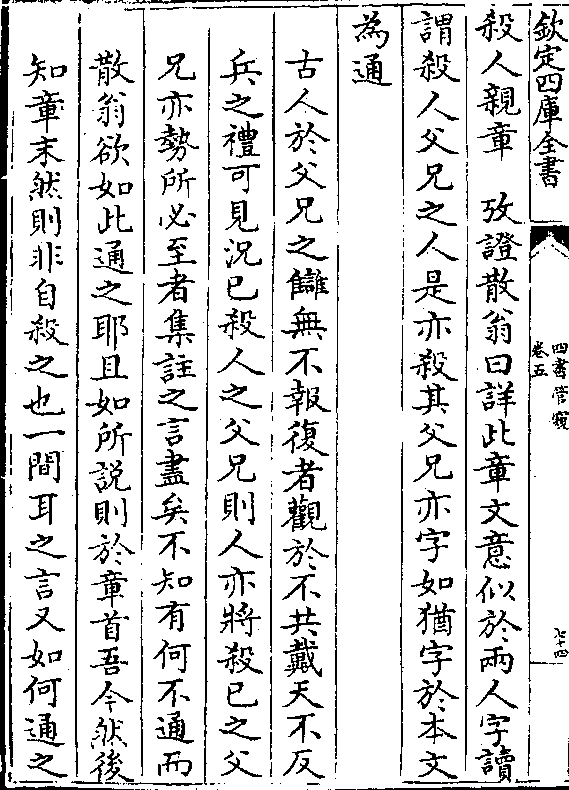 杀人亲章 考證散翁曰详此章文意似于两人字读
杀人亲章 考證散翁曰详此章文意似于两人字读谓杀人父兄之人是亦杀其父兄亦字如犹字于本文
为通
古人于父兄之雠无不报复者观于不共戴天不反
兵之礼可见况已杀人之父兄则人亦将杀己之父
兄亦势所必至者集注之言尽矣不知有何不通而
散翁欲如此通之耶且如所说则于章首吾今然后
知章末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之言又如何通之
卷五 第 75a 页 WYG0204-0847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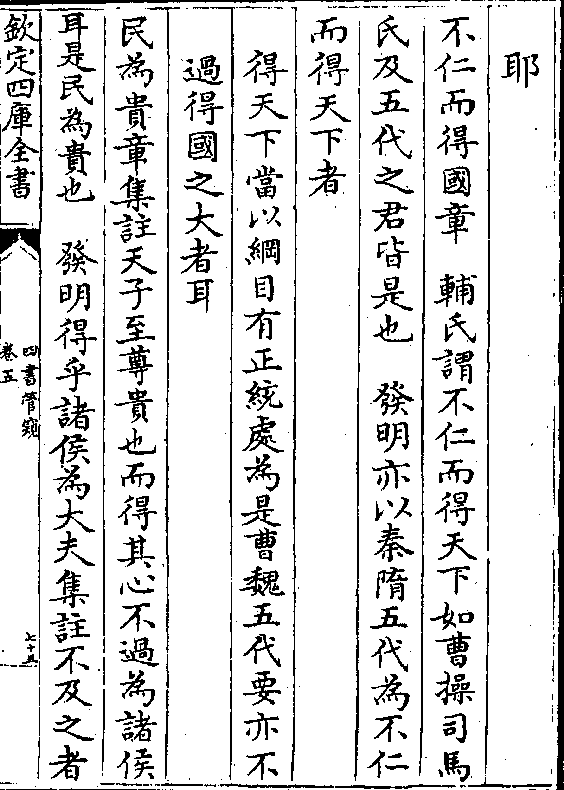 耶
耶不仁而得国章 辅氏谓不仁而得天下如曹操司马
氏及五代之君皆是也 𤼵明亦以秦隋五代为不仁
而得天下者
得天下当以纲目有正统处为是曹魏五代要亦不
过得国之大者耳
民为贵章集注天子至尊贵也而得其心不过为诸侯
耳是民为贵也 𤼵明得乎诸侯为大夫集注不及之者
卷五 第 75b 页 WYG0204-0847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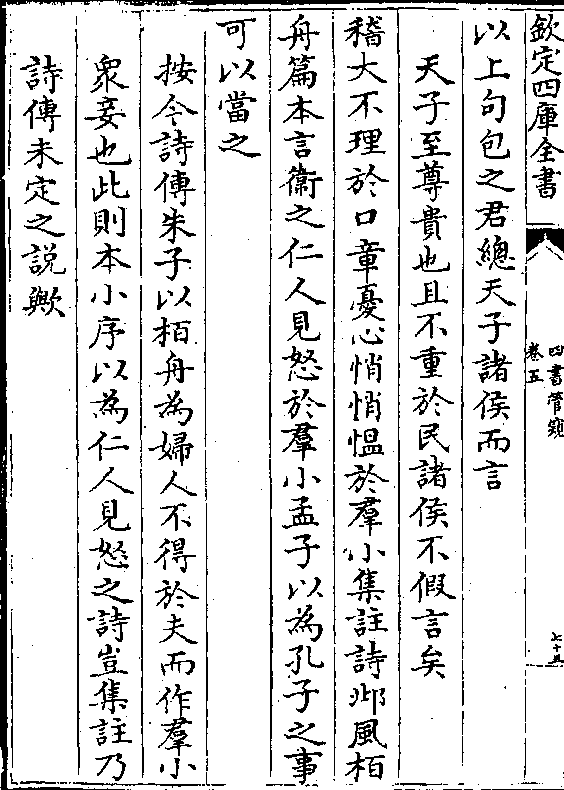 以上句包之君总天子诸侯而言
以上句包之君总天子诸侯而言天子至尊贵也且不重于民诸侯不假言矣
稽大不理于口章忧心悄悄愠于群小集注诗邶风柏
舟篇本言卫之仁人见怒于群小孟子以为孔子之事
可以当之
按今诗传朱子以柏舟为妇人不得于夫而作群小
众妾也此则本小序以为仁人见怒之诗岂集注乃
诗传未定之说欤
卷五 第 76a 页 WYG0204-0848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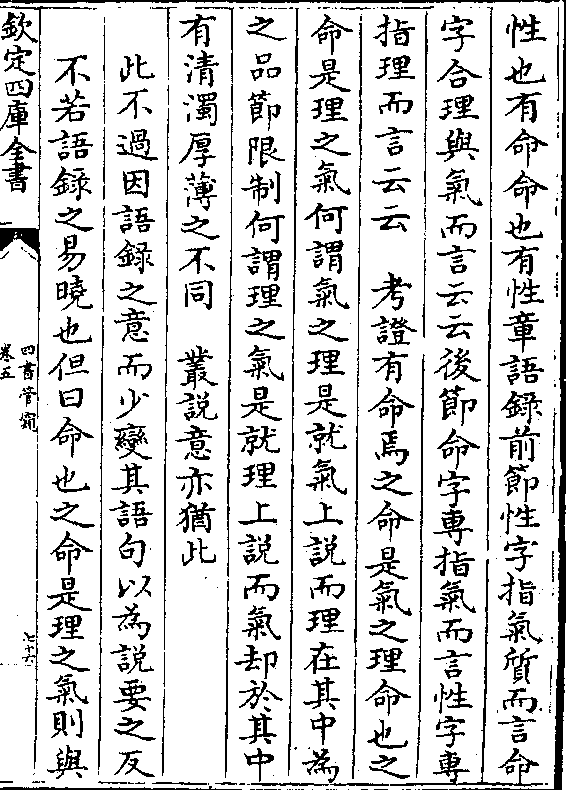 性也有命命也有性章语录前节性字指气质而言命
性也有命命也有性章语录前节性字指气质而言命字合理与气而言云云后节命字专指气而言性字专
指理而言云云 考證有命焉之命是气之理命也之
命是理之气何谓气之理是就气上说而理在其中为
之品节限制何谓理之气是就理上说而气却于其中
有清浊厚薄之不同 丛说意亦犹此
此不过因语录之意而少变其语句以为说要之反
不若语录之易晓也但曰命也之命是理之气则与
卷五 第 76b 页 WYG0204-0848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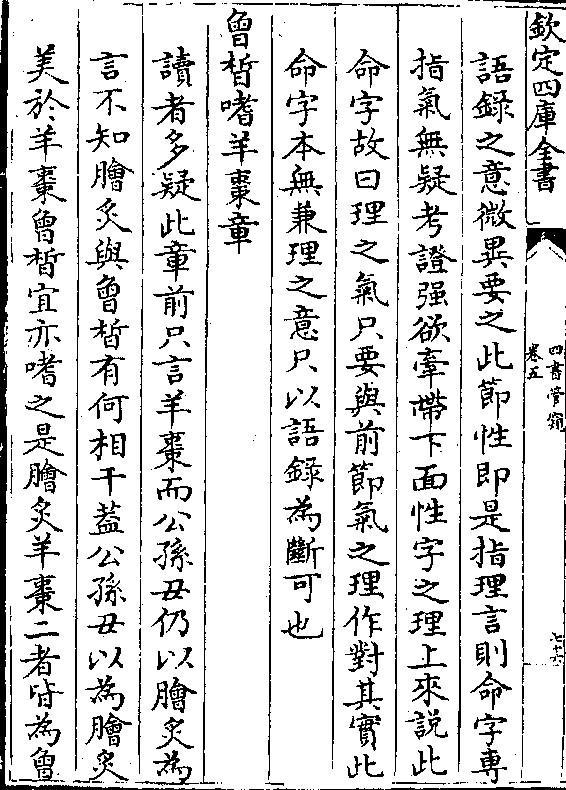 语录之意微异要之此节性即是指理言则命字专
语录之意微异要之此节性即是指理言则命字专指气无疑考證强欲牵带下面性字之理上来说此
命字故曰理之气只要与前节气之理作对其实此
命字本无兼理之意只以语录为断可也
曾晰嗜羊枣章
读者多疑此章前只言羊枣而公孙丑仍以脍炙为
言不知脍炙与曾晰有何相干盖公孙丑以为脍炙
美于羊枣曾晰宜亦嗜之是脍炙羊枣二者皆为曾
卷五 第 77a 页 WYG0204-0848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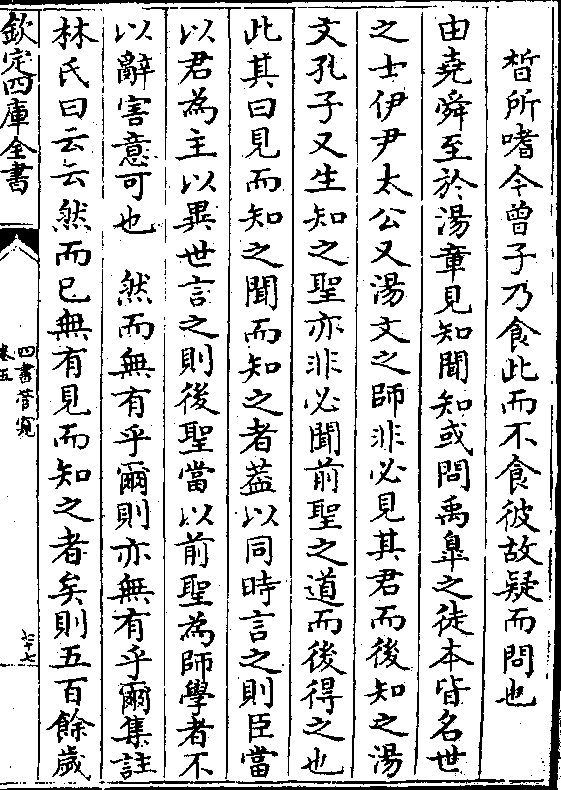 晰所嗜今曾子乃食此而不食彼故疑而问也
晰所嗜今曾子乃食此而不食彼故疑而问也由尧舜至于汤章见知闻知或问禹皋之徒本皆名世
之士伊尹太公又汤文之师非必见其君而后知之汤
文孔子又生知之圣亦非必闻前圣之道而后得之也
此其曰见而知之闻而知之者盖以同时言之则臣当
以君为主以异世言之则后圣当以前圣为师学者不
以辞害意可也 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集注
林氏曰云云然而已无有见而知之者矣则五百馀岁
卷五 第 77b 页 WYG0204-0848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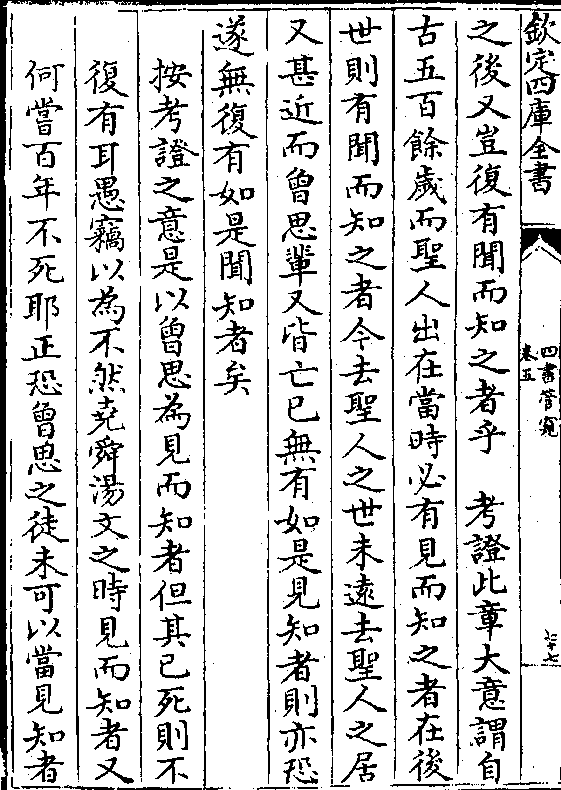 之后又岂复有闻而知之者乎 考證此章大意谓自
之后又岂复有闻而知之者乎 考證此章大意谓自古五百馀岁而圣人出在当时必有见而知之者在后
世则有闻而知之者今去圣人之世未远去圣人之居
又甚近而曾思辈又皆亡已无有如是见知者则亦恐
遂无复有如是闻知者矣
按考證之意是以曾思为见而知者但其已死则不
复有耳愚窃以为不然尧舜汤文之时见而知者又
何尝百年不死耶正恐曾思之徒未可以当见知者
卷五 第 78a 页 WYG0204-0849a.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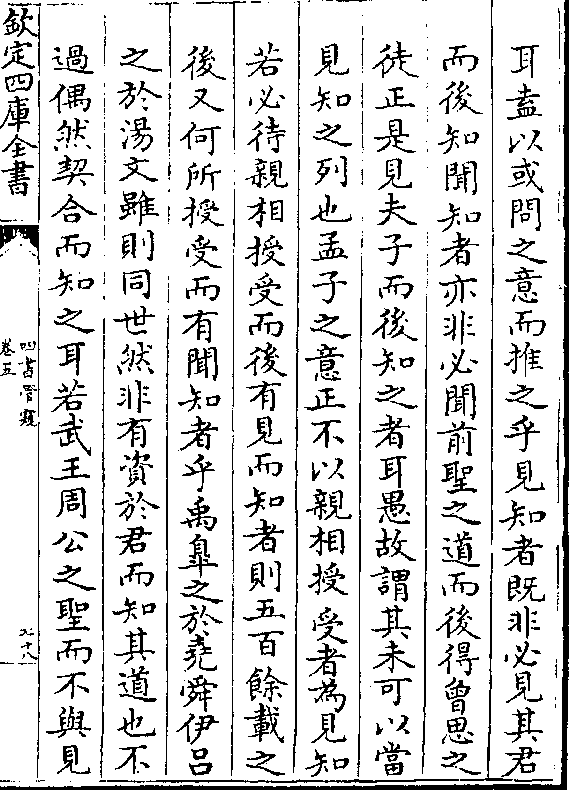 耳盍以或问之意而推之乎见知者既非必见其君
耳盍以或问之意而推之乎见知者既非必见其君而后知闻知者亦非必闻前圣之道而后得曾思之
徒正是见夫子而后知之者耳愚故谓其未可以当
见知之列也孟子之意正不以亲相授受者为见知
若必待亲相授受而后有见而知者则五百馀载之
后又何所授受而有闻知者乎禹皋之于尧舜伊吕
之于汤文虽则同世然非有资于君而知其道也不
过偶然契合而知之耳若武王周公之圣而不与见
卷五 第 78b 页 WYG0204-0849b.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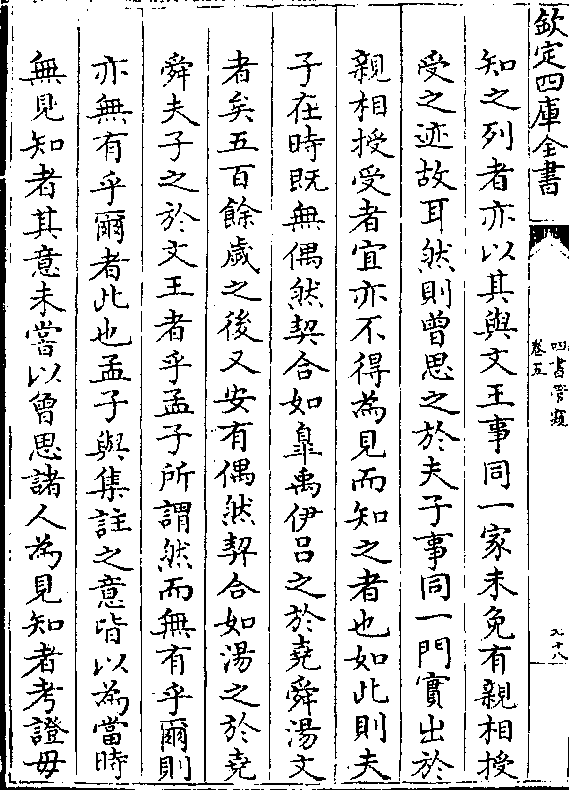 知之列者亦以其与文王事同一家未免有亲相授
知之列者亦以其与文王事同一家未免有亲相授受之迹故耳然则曾思之于夫子事同一门实出于
亲相授受者宜亦不得为见而知之者也如此则夫
子在时既无偶然契合如皋禹伊吕之于尧舜汤文
者矣五百馀岁之后又安有偶然契合如汤之于尧
舜夫子之于文王者乎孟子所谓然而无有乎尔则
亦无有乎尔者此也孟子与集注之意皆以为当时
无见知者其意未尝以曾思诸人为见知者考證毋
卷五 第 79a 页 WYG0204-0849c.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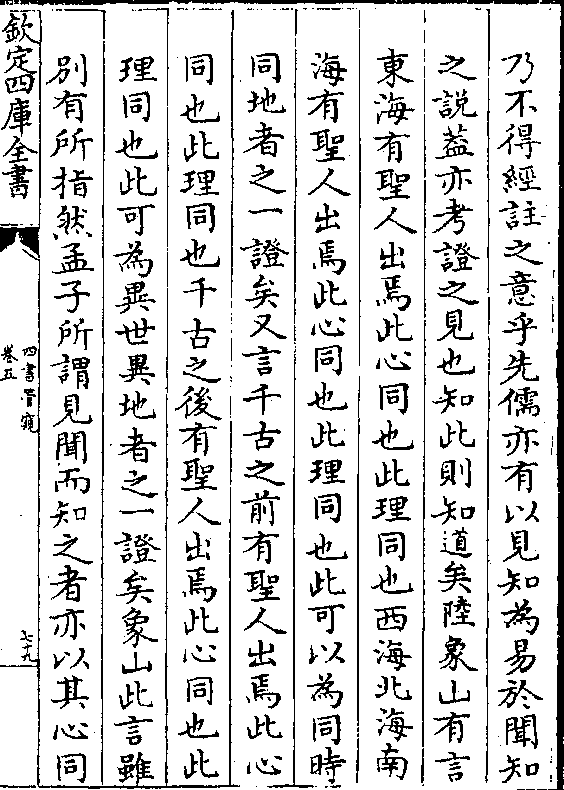 乃不得经注之意乎先儒亦有以见知为易于闻知
乃不得经注之意乎先儒亦有以见知为易于闻知之说盖亦考證之见也知此则知道矣陆象山有言
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北海南
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此可以为同时
同地者之一證矣又言千古之前有圣人出焉此心
同也此理同也千古之后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
理同也此可为异世异地者之一證矣象山此言虽
别有所指然孟子所谓见闻而知之者亦以其心同
卷五 第 79b 页 WYG0204-0849d.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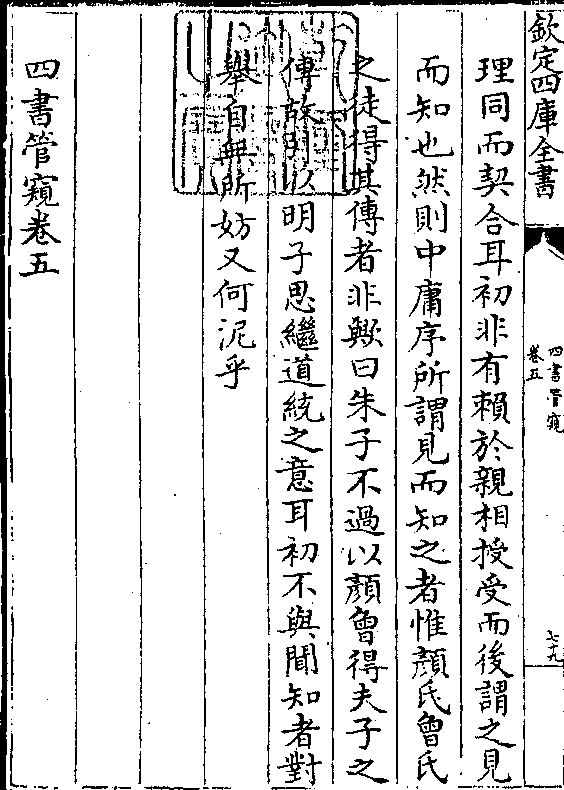 理同而契合耳初非有赖于亲相授受而后谓之见
理同而契合耳初非有赖于亲相授受而后谓之见而知也然则中庸序所谓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
之徒得其传者非欤曰朱子不过以颜曾得夫子之
传故引以明子思继道统之意耳初不与闻知者对
举自无所妨又何泥乎
四书管窥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