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x 页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书
书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81H 页
 上尤庵先生(辛酉四月)
上尤庵先生(辛酉四月)去岁因族叔沃沟之行。修上候书。厥后乃至巧违未达。迨用为恨。伏未审清和。 道体何如。伏慕区区。(侍生)衰病日甚。末由趋拜于 函丈之间。以质胸中之所疑。只切瞻怅而已。前禀瞽说。局于质疑。不自觉其烦渎矣。 警诲至此。不胜惶愧。又以别纸仰禀。 下教至祷。
以人生而静为未发时。自是朱先生之训。而非迷昧之创说也。朱子答严时亨书曰。人生而静。是未发时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时云云。盖人生而静以上。似是一般时节。而分而为二者。猝难晓解。而且以说性为名性。于私心尝窃有所疑矣。又见朱夫子答潘谦之之书。则曰但是性自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只说个善字。所谓天下之言性则故而已者。正谓此也。(答黄商伯杜仁仲书义亦如此)此答与答严书辞旨不同。窃以为此说正合于程夫子之本旨。而乃为后来已定之论也。顷进瞽说。一依朱先生此训。而欲闻归一之论矣。其何敢创立新语。轻议大贤之说乎。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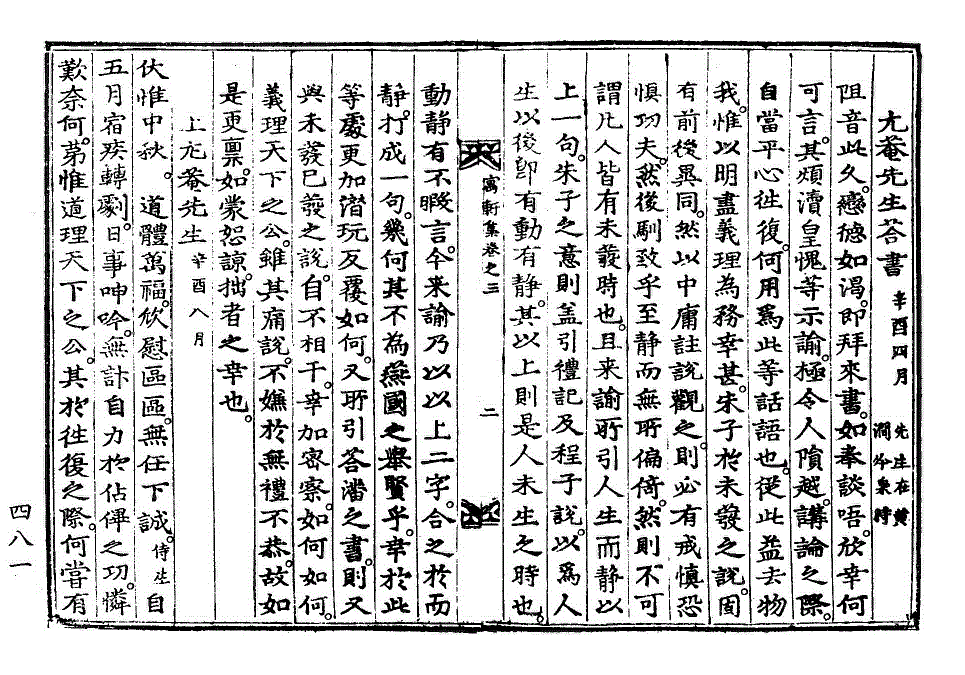 尤庵先生答书(辛酉四月○先生在黄涧冷泉时)
尤庵先生答书(辛酉四月○先生在黄涧冷泉时)阻音此久。恋德如渴。即拜来书。如奉谈唔。欣幸何可言。其烦渎皇愧等示谕。极令人陨越。讲论之际。自当平心往复。何用为此等话语也。从此益去物我。惟以明尽义理为务幸甚。朱子于未发之说。固有前后异同。然以中庸注说观之。则必有戒慎恐惧功夫。然后驯致乎至静而无所偏倚。然则不可谓凡人皆有未发时也。且来谕所引人生而静以上一句。朱子之意则盖引礼记及程子说。以为人生以后即有动有静。其以上则是人未生之时也。动静有不暇言。今来谕乃以以上二字。合之于而静。打成一句。几何其不为燕国之举贤乎。幸于此等处更加潜玩反覆如何。又所引答潘之书。则又与未发已发之说。自不相干。幸加密察。如何如何。义理天下之公。虽其痛说。不嫌于无礼不恭。故如是更禀。如蒙恕谅。拙者之幸也。
上尤庵先生(辛酉八月)
伏惟中秋。 道体万福。欣慰区区。无任下诚。(侍生)自五月宿疾转剧。日事呻吟。无计自力于佔𠌫之功。怜叹奈何。第惟道理天下之公。其于往复之际。何尝有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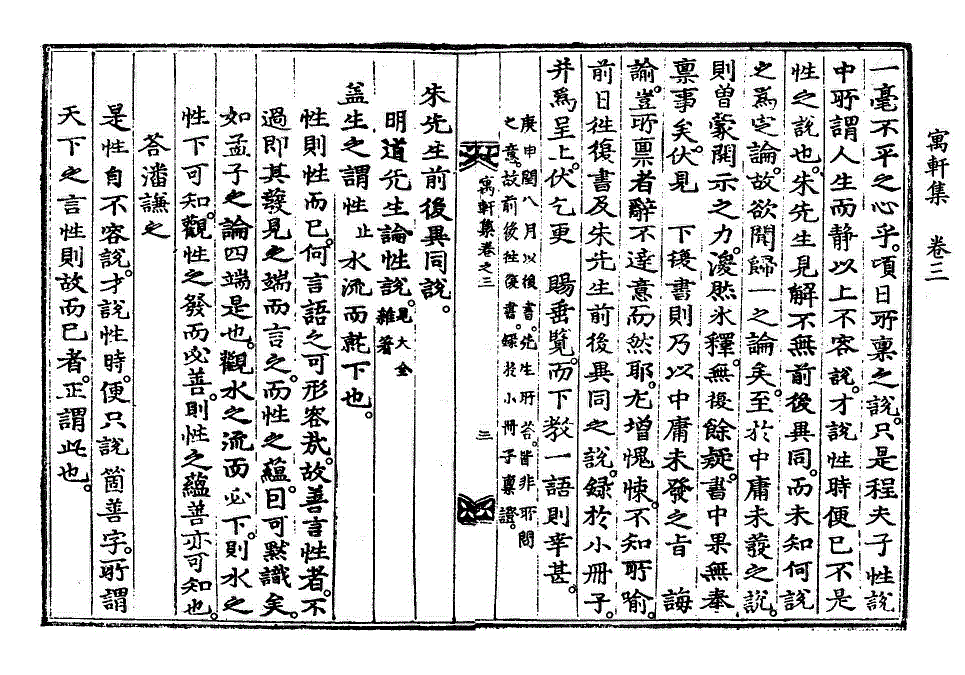 一毫不平之心乎。顷日所禀之说。只是程夫子性说中所谓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之说也。朱先生见解不无前后异同。而未知何说之为定论。故欲闻归一之论矣。至于中庸未发之说。则曾蒙开示之力。涣然冰释。无复馀疑。书中果无奉禀事矣。伏见 下复书则乃以中庸未发之旨 诲谕。岂所禀者辞不达意而然耶。尤增愧悚。不知所喻。前日往复书及朱先生前后异同之说。录于小册子。并为呈上。伏乞更 赐垂览。而下教一语则幸甚。
一毫不平之心乎。顷日所禀之说。只是程夫子性说中所谓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之说也。朱先生见解不无前后异同。而未知何说之为定论。故欲闻归一之论矣。至于中庸未发之说。则曾蒙开示之力。涣然冰释。无复馀疑。书中果无奉禀事矣。伏见 下复书则乃以中庸未发之旨 诲谕。岂所禀者辞不达意而然耶。尤增愧悚。不知所喻。前日往复书及朱先生前后异同之说。录于小册子。并为呈上。伏乞更 赐垂览。而下教一语则幸甚。(庚申闰八月以后书。先生所答。皆非所问之意。故前后往复书。录于小册子禀證。)
朱先生前后异同说。
明道先生论性说。(见大全杂著)
盖生之谓性(止)水流而就下也。
性则性而已。何言语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过即其发见之端而言之。而性之蕴。因可默识矣。如孟子之论四端是也。观水之流而必下。则水之性下可知。观性之发而必善。则性之蕴善亦可知也。
答潘谦之
是性自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只说个善字。所谓天下之言性则故而已者。正谓此也。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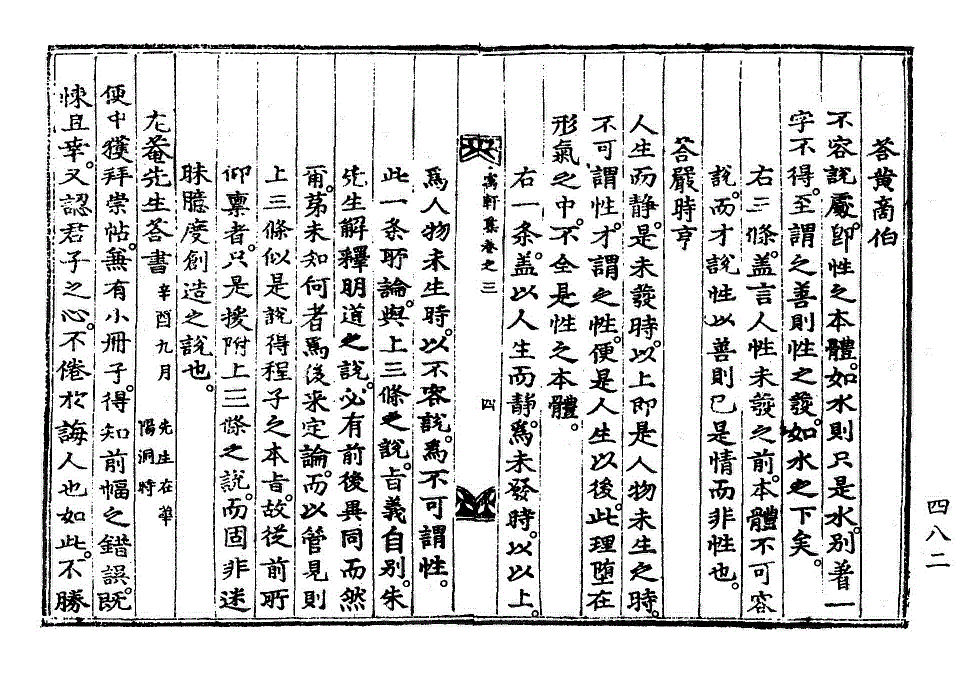 答黄商伯
答黄商伯不容说处。即性之本体。如水则只是水。别着一字不得。至谓之善则性之发。如水之下矣。
右三条。盖言人性未发之前。本体不可容说。而才说性以善则已是情而非性也。
答严时亨
人生而静。是未发时。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时。不可谓性。才谓之性。便是人生以后。此理堕在形气之中。不全是性之本体。
右一条。盖以人生而静。为未发时。以以上。为人物未生时。以不容说。为不可谓性。
此一条所论。与上三条之说。旨义自别。朱先生解释明道之说。必有前后异同而然尔。第未知何者为后来定论。而以管见则上三条似是说得程子之本旨。故从前所仰禀者。只是援附上三条之说。而固非迷昧臆度创造之说也。
尤庵先生答书(辛酉九月○先生在华阳洞时)
便中获拜崇帖。兼有小册子。得知前幅之错误。既悚且幸。又认君子之心。不倦于诲人也如此。不胜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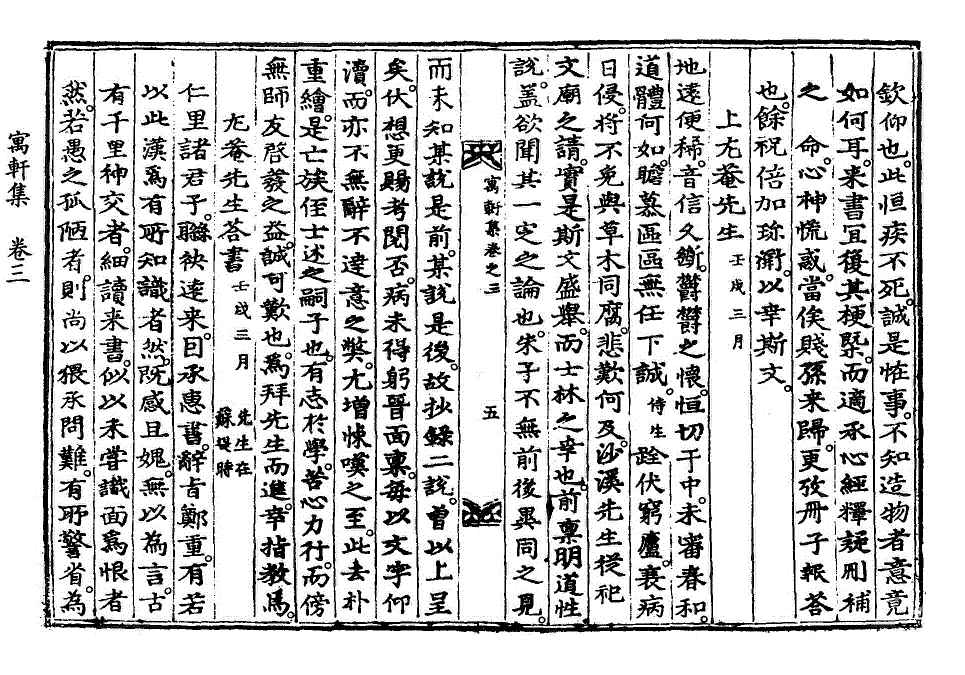 钦仰也。此恒疾不死。诚是怪事。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耳。来书宜复其梗槩。而适承心经释疑删补之 命。心神慌惑。当俟贱孙来归。更考册子报答也。馀祝倍加珍卫。以幸斯文。
钦仰也。此恒疾不死。诚是怪事。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耳。来书宜复其梗槩。而适承心经释疑删补之 命。心神慌惑。当俟贱孙来归。更考册子报答也。馀祝倍加珍卫。以幸斯文。上尤庵先生(壬戌三月)
地远便稀。音信久断。郁郁之怀。恒切于中。未审春和。道体何如。瞻慕区区无任下诚。(侍生)跧伏穷庐。衰病日侵。将不免与草木同腐。悲叹何及。沙溪先生从祀 文庙之请。实是斯文盛举。而士林之幸也。前禀明道性说。盖欲闻其一定之论也。朱子不无前后异同之见。而未知某说是前。某说是后。故抄录二说。曾以上呈矣。伏想更赐考阅否。病未得躬晋面禀。每以文字仰渎。而亦不无辞不达意之弊。尤增悚叹之至。此去朴重绘。是亡族侄士述之嗣子也。有志于学。苦心力行。而傍无师友启发之益。诚可叹也。为拜先生而进。幸指教焉。
尤庵先生答书(壬戌三月○先生在苏堤时)
仁里诸君子。联袂远来。因承惠书。辞旨郑重。有若以此汉为有所知识者然。既感且愧。无以为言。古有千里神交者。细读来书。似以未尝识面为恨者然。若愚之孤陋者。则尚以猥承问难。有所警省。为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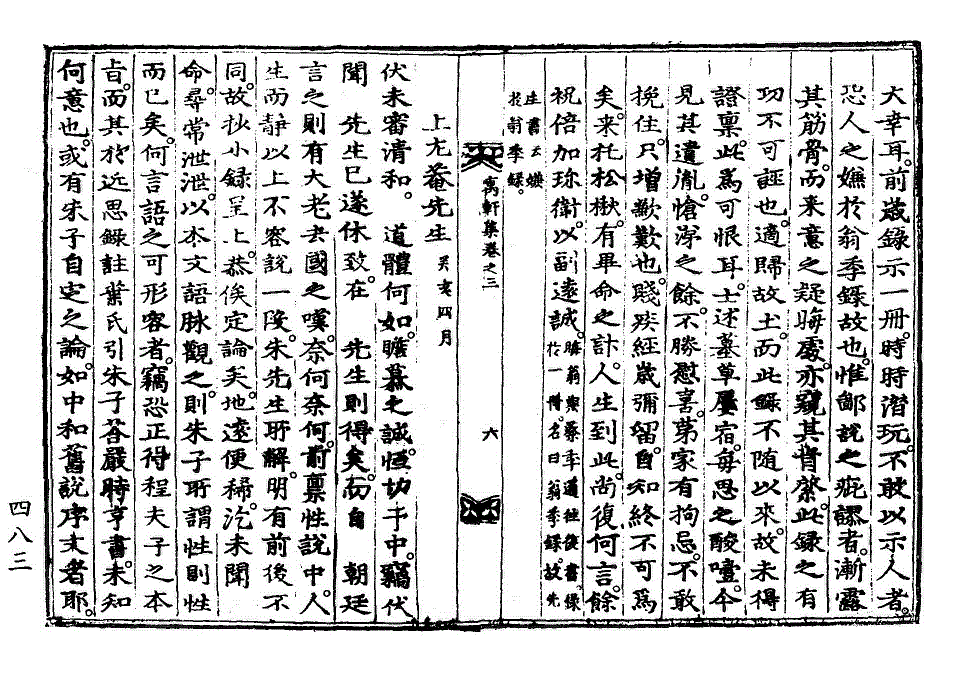 大幸耳。前岁录示一册。时时潜玩。不敢以示人者。恐人之嫌于翁季录故也。惟鄙说之疵谬者。渐露其筋骨。而来意之疑晦处。亦窥其肯綮。此录之有功不可诬也。适归故土。而此录不随以来。故未得證禀。此为可恨耳。士述墓草屡宿。每思之酸噎。今见其遗胤。怆涕之馀。不胜慰喜。第家有拘忌。不敢挽住。只增歉叹也。贱疾经岁弥留。自知终不可为矣。来托松楸。有毕命之计。人生到此。尚复何言。馀祝倍加珍卫。以副远诚。(晦翁与蔡季通往复书。录于一册。名曰翁季录。故先生书云嫌于翁季录。)
大幸耳。前岁录示一册。时时潜玩。不敢以示人者。恐人之嫌于翁季录故也。惟鄙说之疵谬者。渐露其筋骨。而来意之疑晦处。亦窥其肯綮。此录之有功不可诬也。适归故土。而此录不随以来。故未得證禀。此为可恨耳。士述墓草屡宿。每思之酸噎。今见其遗胤。怆涕之馀。不胜慰喜。第家有拘忌。不敢挽住。只增歉叹也。贱疾经岁弥留。自知终不可为矣。来托松楸。有毕命之计。人生到此。尚复何言。馀祝倍加珍卫。以副远诚。(晦翁与蔡季通往复书。录于一册。名曰翁季录。故先生书云嫌于翁季录。)上尤庵先生(癸亥四月)
伏未审清和。 道体何如。瞻慕之诚。恒切于中。窃伏闻 先生已遂休致。在 先生则得矣。而自 朝廷言之则有大老去国之叹。奈何奈何。前禀性说中。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一段。朱先生所解。明有前后不同。故抄小录呈上。恭俟定论矣。地远便稀。汔未闻 命。寻常泄泄。以本文语脉观之。则朱子所谓性则性而已矣。何言语之可形容者。窃恐正得程夫子之本旨。而其于近思录注叶氏引朱子答严时亨书。未知何意也。或有朱子自定之论。如中和旧说序文者耶。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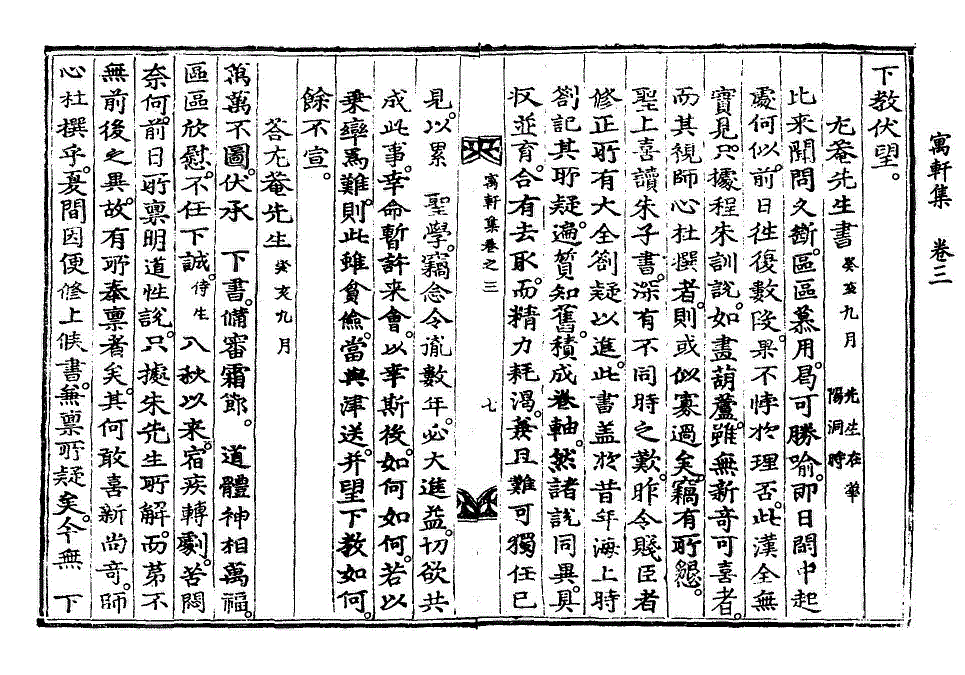 下教伏望。
下教伏望。尤庵先生书(癸亥九月○先生在华阳洞时)
比来闻问久断。区区慕用。曷可胜喻。即日闲中起处何似。前日往复数段。果不悖于理否。此汉全无实见。只据程朱训说。如画葫芦。虽无新奇可喜者。而其视师心杜撰者。则或似寡过矣。窃有所恳。 圣上喜读朱子书。深有不同时之叹。昨令贱臣者修正所有大全劄疑以进。此书盖于昔年海上时劄记其所疑。遍质知旧。积成卷轴。然诸说同异。具收并育。合有去取。而精力耗渴。兼且难可独任己见。以累 圣学。窃念令胤数年。必大进益。切欲共成此事。幸命暂许来会。以幸斯后。如何如何。若以乘率为难。则此虽贫俭。当与津送。并望下教如何。馀不宣。
答尤庵先生(癸亥九月)
万万不图。伏承 下书。备审霜节。 道体神相万福。区区欣慰。不任下诚。(侍生)入秋以来。宿疾转剧。苦闷奈何。前日所禀明道性说。只据朱先生所解。而第不无前后之异。故有所奉禀者矣。其何敢喜新尚奇。师心杜撰乎。夏间因便修上候书。兼禀所疑矣。今无 下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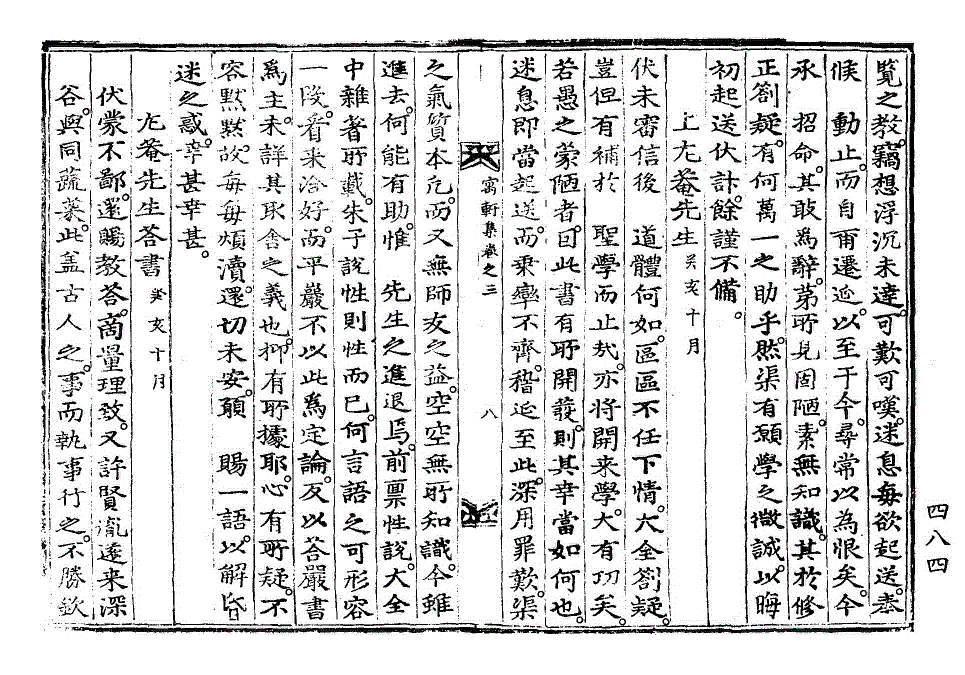 览之教。窃想浮沈未达。可叹可叹。迷息每欲起送。奉候 动止。而自尔迁延。以至于今。寻常以为恨矣。今承 招命。其敢为辞。第所见固陋。素无知识。其于修正劄疑。有何万一之助乎。然渠有愿学之微诚。以晦初起送伏计。馀谨不备。
览之教。窃想浮沈未达。可叹可叹。迷息每欲起送。奉候 动止。而自尔迁延。以至于今。寻常以为恨矣。今承 招命。其敢为辞。第所见固陋。素无知识。其于修正劄疑。有何万一之助乎。然渠有愿学之微诚。以晦初起送伏计。馀谨不备。上尤庵先生(癸亥十月)
伏未审信后 道体何如。区区不任下情。大全劄疑。岂但有补于 圣学而止哉。亦将开来学。大有功矣。若愚之蒙陋者。因此书有所开发。则其幸当如何也。迷息即当起送。而乘率不齐。稽延至此。深用罪叹。渠之气质本凡。而又无师友之益。空空无所知识。今虽进去。何能有助。惟 先生之进退焉。前禀性说。大全中杂著所载。朱子说性则性而已。何言语之可形容一段。看来洽好。而平岩不以此为定论。反以答严书为主。未详其取舍之义也。抑有所据耶。心有所疑。不容默默。故每每烦渎。还切未安。愿 赐一语。以解昏迷之惑。幸甚幸甚。
尤庵先生答书(癸亥十月)
伏蒙不鄙。还赐教答。商量理致。又许贤胤远来深谷。与同蔬菜。此盖古人之。事而执事行之。不胜钦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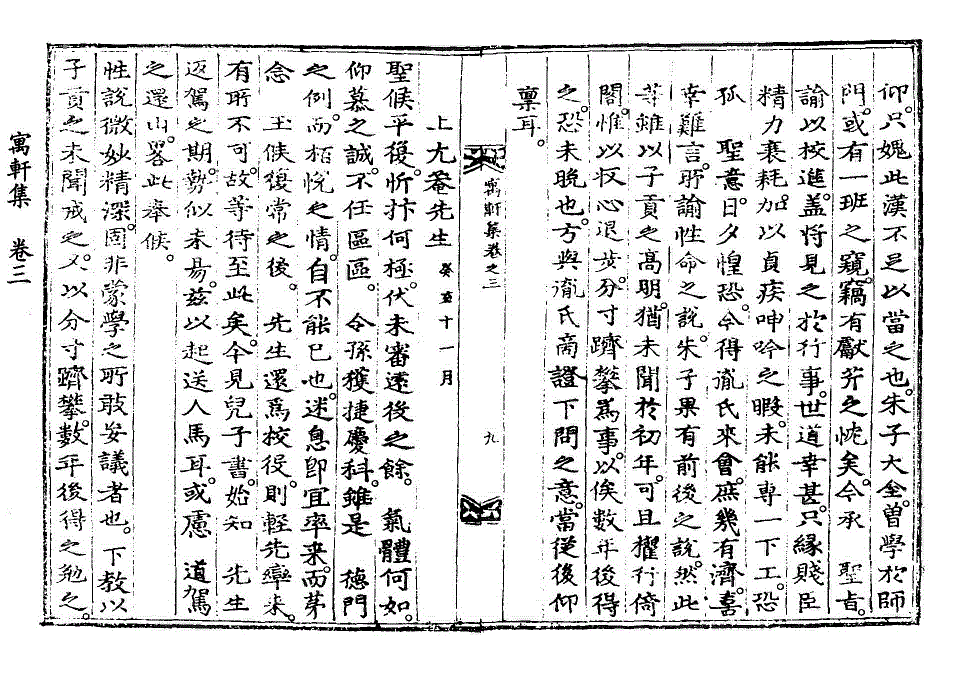 仰。只愧此汉不足以当之也。朱子大全。曾学于师门。或有一班之窥。窃有献芹之忱矣。今承 圣旨。谕以校进。盖将见之于行事。世道幸甚。只缘贱臣精力衰耗。加以贞疾呻吟之暇。未能专一下工。恐孤 圣意。日夕惶恐。今得胤氏来会。庶几有济。喜幸难言。所谕性命之说。朱子果有前后之说。然此等虽以子贡之高明。犹未闻于初年。可且权行倚阁。惟以收心退步。分寸跻攀为事。以俟数年后得之。恐未晚也。方与胤氏商證下问之意。当从后仰禀耳。
仰。只愧此汉不足以当之也。朱子大全。曾学于师门。或有一班之窥。窃有献芹之忱矣。今承 圣旨。谕以校进。盖将见之于行事。世道幸甚。只缘贱臣精力衰耗。加以贞疾呻吟之暇。未能专一下工。恐孤 圣意。日夕惶恐。今得胤氏来会。庶几有济。喜幸难言。所谕性命之说。朱子果有前后之说。然此等虽以子贡之高明。犹未闻于初年。可且权行倚阁。惟以收心退步。分寸跻攀为事。以俟数年后得之。恐未晚也。方与胤氏商證下问之意。当从后仰禀耳。上尤庵先生(癸亥十一月)
圣候平复。忻抃何极。伏未审远役之馀。 气体何如。仰慕之诚。不任区区。 令孙获捷庆科。虽是 德门之例。而柏悦之情。自不能已也。迷息即宜率来。而第念 玉候复常之后。 先生还为校役。则轻先率来。有所不可。故等待至此矣。今见儿子书。始知 先生返驾之期。势似未易。玆以起送人马耳。或虑 道驾之还山。略此奉候。
性说微妙精深。固非蒙学之所敢妄议者也。下教以子贡之未闻戒之。又以分寸跻攀。数年后得之勉之。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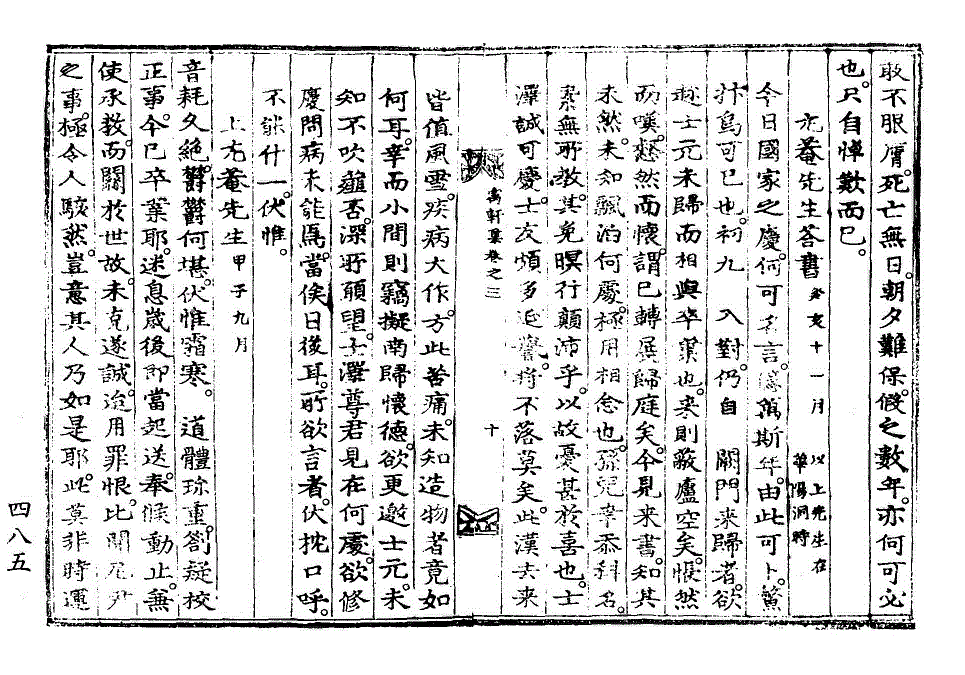 敢不服屑。死亡无日。朝夕难保。假之数年。亦何可必也。只自悼叹而已。
敢不服屑。死亡无日。朝夕难保。假之数年。亦何可必也。只自悼叹而已。尤庵先生答书(癸亥十一月○以上先生在华阳洞时)
今日国家之庆。何可名言。亿万斯年。由此可卜。鳌抃乌可已也。初九 入对。仍自 阙门来归者。欲趁士元未归而相与卒业也。来则蔽庐空矣。怅然而叹。惄然而怀。谓已转展归庭矣。今见来书。知其未然。未知飘泊何处。极用相念也。孙儿幸忝科名。素无所教。其免暝行颠沛乎。以故忧甚于喜也。士泽诚可庆。士友颇多延誉。将不落莫矣。此汉去来皆值风雪。疾病大作。方此苦痛。未知造物者竟如何耳。幸而小间则窃拟南归怀德。欲更邀士元。未知不吹歼否。深所愿望。士泽尊君见在何处。欲修庆问病未能焉。当俟日后耳。所欲言者。伏枕口呼。不能什一。伏惟。
上尤庵先生(甲子九月)
音耗久绝。郁郁何堪。伏惟霜寒。 道体珍重。劄疑校正事。今已卒业耶。迷息岁后即当起送。奉候动止。兼使承教。而关于世故。未克遂诚。迨用罪恨。比闻尼尹之事。极令人骇然。岂意其人乃如是耶。此莫非时运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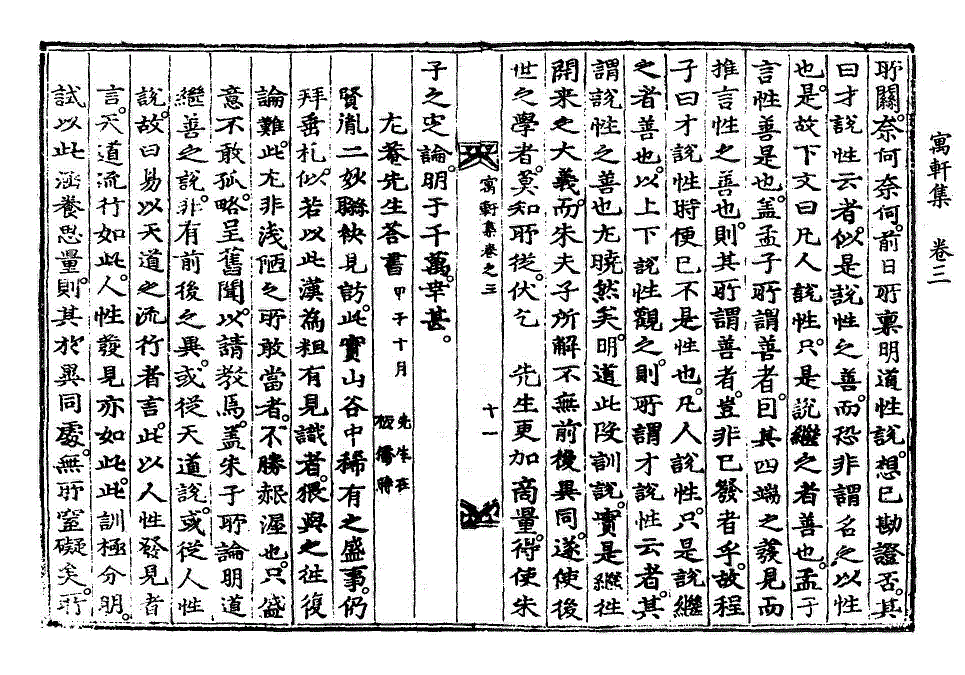 所关。奈何奈何。前日所禀明道性说。想已勘證否。其曰才说性云者。似是说性之善。而恐非谓名之以性也。是故下文曰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盖孟子所谓善者。因其四端之发见而推言性之善也。则其所谓善者。岂非已发者乎。故程子曰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以上下说性观之。则所谓才说性云者。其谓说性之善也尤晓然矣。明道此段训说。实是继往开来之大义。而朱夫子所解不无前后异同。遂使后世之学者。莫知所从。伏乞 先生更加商量。得使朱子之定论。明于千万。幸甚。
所关。奈何奈何。前日所禀明道性说。想已勘證否。其曰才说性云者。似是说性之善。而恐非谓名之以性也。是故下文曰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盖孟子所谓善者。因其四端之发见而推言性之善也。则其所谓善者。岂非已发者乎。故程子曰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以上下说性观之。则所谓才说性云者。其谓说性之善也尤晓然矣。明道此段训说。实是继往开来之大义。而朱夫子所解不无前后异同。遂使后世之学者。莫知所从。伏乞 先生更加商量。得使朱子之定论。明于千万。幸甚。尤庵先生答书(甲子十月○先生在板侨时)
贤胤二妙联袂见访。此实山谷中稀有之盛事。仍拜垂札。似若以此汉为粗有见识者。猥与之往复论难。此尤非浅陋之所敢当者。不胜赧渥也。只盛意不敢孤。略呈旧闻。以请教焉。盖朱子所论明道继善之说。非有前后之异。或从天道说。或从人性说。故曰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发见者言。天道流行如此。人性发见亦如此。此训极分明。试以此涵养思量。则其于异同处。无所窒碍矣。所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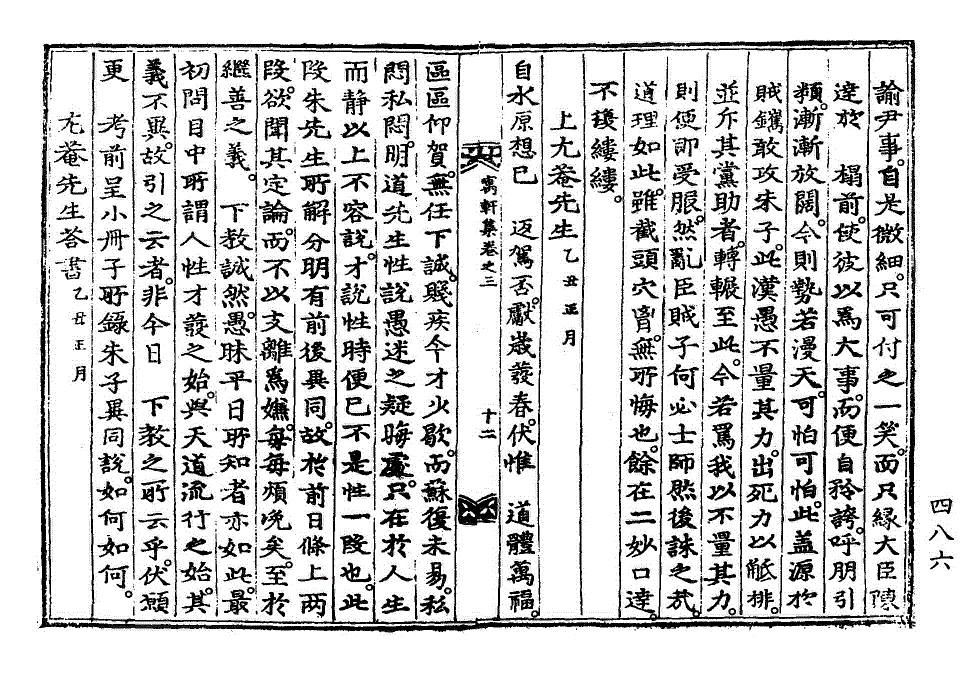 谕尹事。自是微细。只可付之一笑。而只缘大臣陈达于 榻前。使彼以为大事。而便自矜誇。呼朋引类。渐渐放阔。今则势若漫天。可怕可怕。此盖源于贼鑴敢攻朱子。此汉愚不量其力。出死力以抵排。并斥其党助者。转辗至此。今若骂我以不量其力。则便即受服。然乱臣贼子何必士师然后诛之哉。道理如此。虽截头穴胸。无所悔也。馀在二妙口达。不复缕缕。
谕尹事。自是微细。只可付之一笑。而只缘大臣陈达于 榻前。使彼以为大事。而便自矜誇。呼朋引类。渐渐放阔。今则势若漫天。可怕可怕。此盖源于贼鑴敢攻朱子。此汉愚不量其力。出死力以抵排。并斥其党助者。转辗至此。今若骂我以不量其力。则便即受服。然乱臣贼子何必士师然后诛之哉。道理如此。虽截头穴胸。无所悔也。馀在二妙口达。不复缕缕。上尤庵先生(乙丑正月)
自水原想已 返驾否。献岁发春。伏惟 道体万福。区区仰贺。无任下诚。贱疾今才少歇。而苏复未易。私闷私闷。明道先生性说愚迷之疑晦处。只在于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一段也。此段朱先生所解分明有前后异同。故于前日条上两段。欲闻其定论。而不以支离为嫌。每每烦浼矣。至于继善之义。 下教诚然。愚昧平日所知者亦如此。最初问目中所谓人性才发之始。与天道流行之始。其义不异。故引之云者。非今日 下教之所云乎。伏愿更 考前呈小册子所录朱子异同说。如何如何。
尤庵先生答书(乙丑五月)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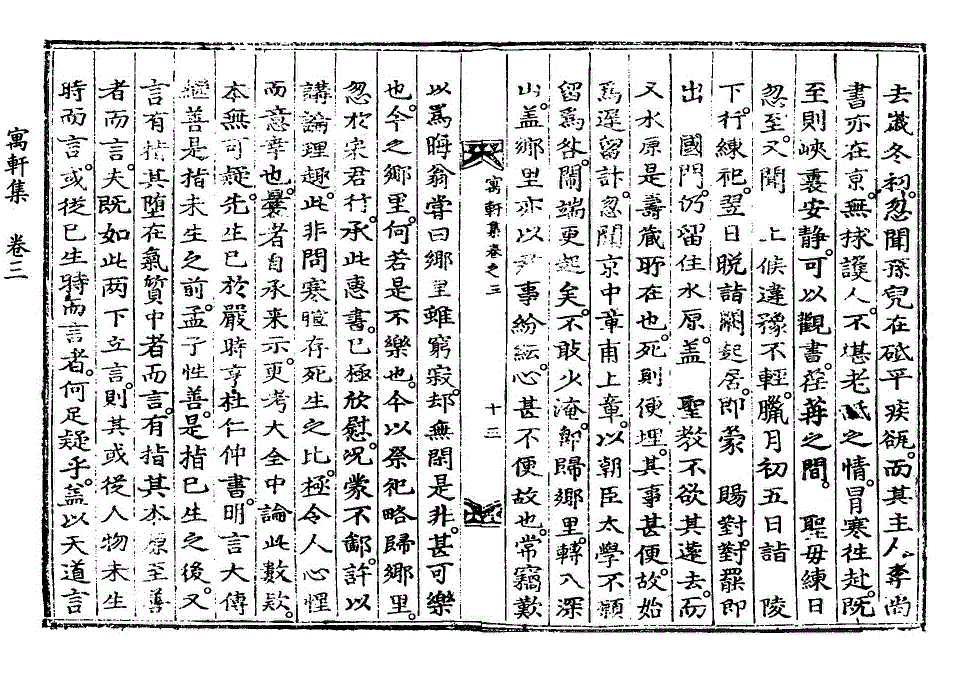 去岁冬初。忽闻孙儿在砥平疾谻。而其主人李尚书亦在京。无救护人。不堪老舐之情。冒寒往赴。既至则峡里安静。可以观书。荏苒之间。 圣母练日忽至。又闻 上候违豫不轻。腊月初五日诣 陵下。行练祀。翌日晚诣阙起居。即蒙 赐对。对罢即出 国门。仍留住水原。盖 圣教不欲其远去。而又水原是寿藏所在也。死则便埋。其事甚便。故始为迟留计。忽闻京中章甫上章。以朝臣太学不愿留为咎。闹端更起矣。不敢少淹。即归乡里。转入深山。盖乡里亦以尹事纷纭。心甚不便故也。常窃叹以为晦翁尝曰乡里虽穷寂。却无闲是非。甚可乐也。今之乡里。何若是不乐也。今以祭祀略归乡里。忽于宋君行。承此惠书。已极欣慰。况蒙不鄙。许以讲论理趣。此非问寒暄存死生之比。极令人心惺而意幸也。曩者自承来示。更考大全中论此数款。本无可疑。先生已于严时亨,杜仁仲书。明言大传继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性善。是指已生之后。又言有指其堕在气质中者而言。有指其本原至善者而言。夫既如此两下立言。则其或从人物未生时而言。或从已生时而言者。何足疑乎。盖以天道言
去岁冬初。忽闻孙儿在砥平疾谻。而其主人李尚书亦在京。无救护人。不堪老舐之情。冒寒往赴。既至则峡里安静。可以观书。荏苒之间。 圣母练日忽至。又闻 上候违豫不轻。腊月初五日诣 陵下。行练祀。翌日晚诣阙起居。即蒙 赐对。对罢即出 国门。仍留住水原。盖 圣教不欲其远去。而又水原是寿藏所在也。死则便埋。其事甚便。故始为迟留计。忽闻京中章甫上章。以朝臣太学不愿留为咎。闹端更起矣。不敢少淹。即归乡里。转入深山。盖乡里亦以尹事纷纭。心甚不便故也。常窃叹以为晦翁尝曰乡里虽穷寂。却无闲是非。甚可乐也。今之乡里。何若是不乐也。今以祭祀略归乡里。忽于宋君行。承此惠书。已极欣慰。况蒙不鄙。许以讲论理趣。此非问寒暄存死生之比。极令人心惺而意幸也。曩者自承来示。更考大全中论此数款。本无可疑。先生已于严时亨,杜仁仲书。明言大传继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性善。是指已生之后。又言有指其堕在气质中者而言。有指其本原至善者而言。夫既如此两下立言。则其或从人物未生时而言。或从已生时而言者。何足疑乎。盖以天道言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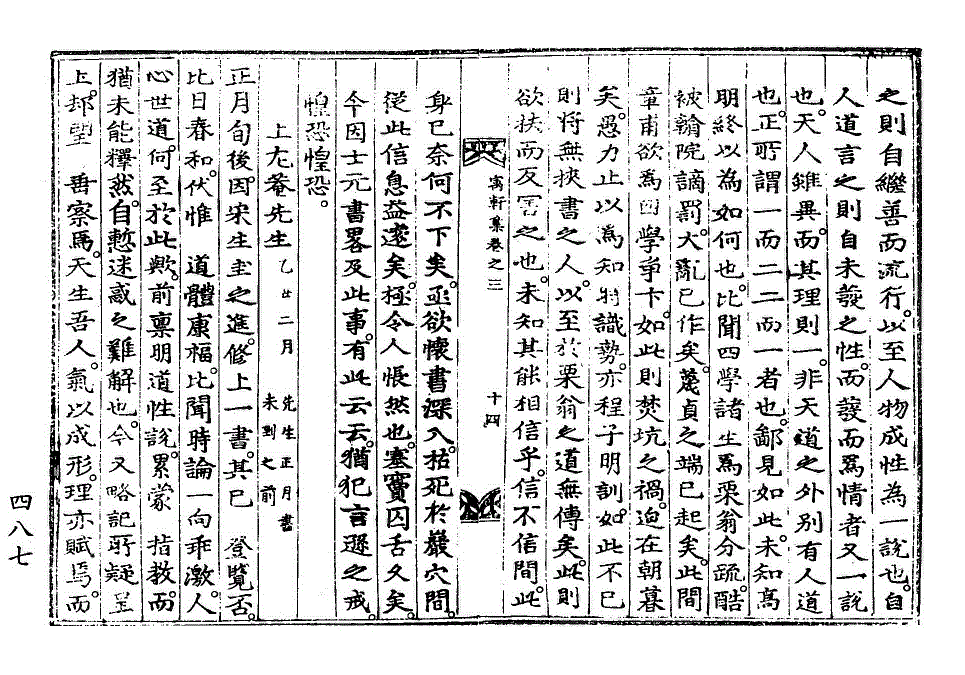 之则自继善而流行。以至人物成性为一说也。自人道言之则自未发之性。而发而为情者又一说也。天人虽异。而其理则一。非天道之外别有人道也。正所谓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鄙见如此。未知高明终以为如何也。比闻四学诸生为栗翁分疏。酷被翰院谪罚。大乱已作矣。蔑贞之端已起矣。此间章甫欲为四学争卞。如此则焚坑之祸。迫在朝暮矣。愚力止以为知时识势。亦程子明训。如此不已则将无挟书之人。以至于栗翁之道无传矣。此则欲扶而反害之也。未知其能相信乎。信不信间。此身已奈何不下矣。亟欲怀书深入。枯死于岩穴间。从此信息益远矣。极令人怅然也。塞窦囚舌久矣。今因士元书略及此事。有此云云。犹犯言逊之戒。惶恐惶恐。
之则自继善而流行。以至人物成性为一说也。自人道言之则自未发之性。而发而为情者又一说也。天人虽异。而其理则一。非天道之外别有人道也。正所谓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鄙见如此。未知高明终以为如何也。比闻四学诸生为栗翁分疏。酷被翰院谪罚。大乱已作矣。蔑贞之端已起矣。此间章甫欲为四学争卞。如此则焚坑之祸。迫在朝暮矣。愚力止以为知时识势。亦程子明训。如此不已则将无挟书之人。以至于栗翁之道无传矣。此则欲扶而反害之也。未知其能相信乎。信不信间。此身已奈何不下矣。亟欲怀书深入。枯死于岩穴间。从此信息益远矣。极令人怅然也。塞窦囚舌久矣。今因士元书略及此事。有此云云。犹犯言逊之戒。惶恐惶恐。上尤庵先生(乙丑二月○先生正月书未到之前)
正月旬后。因宋生圭之进。修上一书。其已 登览否。比日春和。伏惟 道体康福。比闻时论一向乖激。人心世道。何至于此欤。前禀明道性说。累蒙 指教。而犹未能释然。自惭迷惑之难解也。今又略记所疑呈上。却望 垂察焉。天生吾人。气以成形。理亦赋焉。而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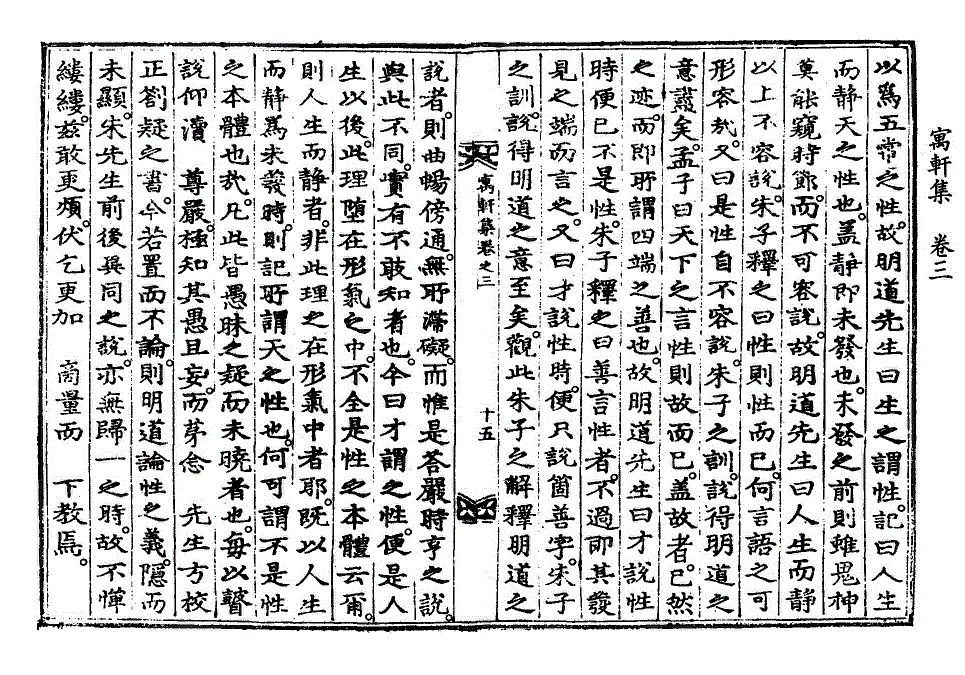 以为五常之性。故明道先生曰生之谓性。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盖静即未发也。未发之前则虽鬼神莫能窥时节。而不可容说。故明道先生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朱子释之曰性则性而已。何言语之可形容哉。又曰是性自不容说。朱子之训。说得明道之意尽矣。孟子曰天下之言性则故而已。盖故者。已然之迹。而即所谓四端之善也。故明道先生曰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朱子释之曰善言性者。不过即其发见之端而言之。又曰才说性时。便只说个善字。朱子之训。说得明道之意至矣。观此朱子之解释明道之说者。则曲畅傍通。无所滞碍。而惟是答严时亨之说。与此不同。实有不敢知者也。今曰才谓之性。便是人生以后。此理堕在形气之中。不全是性之本体云尔。则人生而静者。非此理之在形气中者耶。既以人生而静为未发时。则记所谓天之性也。何可谓不是性之本体也哉。凡此皆愚昧之疑而未晓者也。每以瞽说仰渎 尊严。极知其愚且妄。而第念 先生方校正劄疑之书。今若置而不论。则明道论性之义。隐而未显。朱先生前后异同之说。亦无归一之时。故不惮缕缕。兹敢更烦。伏乞更加 商量而 下教焉。
以为五常之性。故明道先生曰生之谓性。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盖静即未发也。未发之前则虽鬼神莫能窥时节。而不可容说。故明道先生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朱子释之曰性则性而已。何言语之可形容哉。又曰是性自不容说。朱子之训。说得明道之意尽矣。孟子曰天下之言性则故而已。盖故者。已然之迹。而即所谓四端之善也。故明道先生曰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朱子释之曰善言性者。不过即其发见之端而言之。又曰才说性时。便只说个善字。朱子之训。说得明道之意至矣。观此朱子之解释明道之说者。则曲畅傍通。无所滞碍。而惟是答严时亨之说。与此不同。实有不敢知者也。今曰才谓之性。便是人生以后。此理堕在形气之中。不全是性之本体云尔。则人生而静者。非此理之在形气中者耶。既以人生而静为未发时。则记所谓天之性也。何可谓不是性之本体也哉。凡此皆愚昧之疑而未晓者也。每以瞽说仰渎 尊严。极知其愚且妄。而第念 先生方校正劄疑之书。今若置而不论。则明道论性之义。隐而未显。朱先生前后异同之说。亦无归一之时。故不惮缕缕。兹敢更烦。伏乞更加 商量而 下教焉。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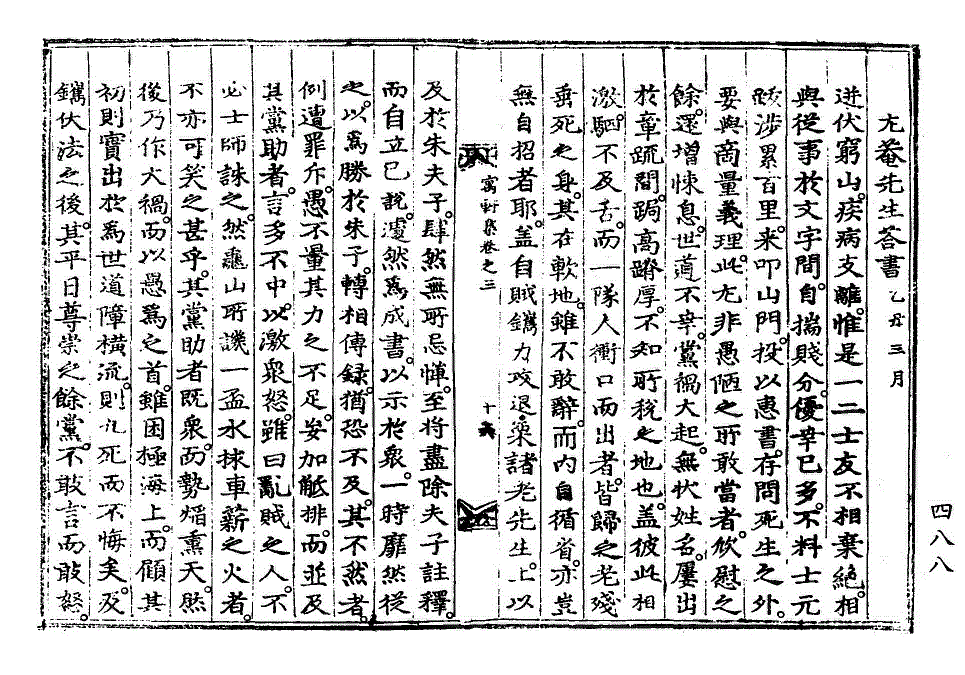 尤庵先生答书(乙丑三月)
尤庵先生答书(乙丑三月)迸伏穷山。疾病支离。惟是一二士友不相弃绝。相与从事于文字间。自揣贱分。优幸已多。不料士元跋涉累百里。来叩山门。投以惠书。存问死生之外。要与商量义理。此尤非愚陋之所敢当者。欣慰之馀。还增悚息。世道不幸。党祸大起。无状姓名。屡出于章疏间。跼高蹐厚。不知所税之地也。盖彼此相激。驷不及舌。而一队人冲口而出者。皆归之老残垂死之身。其在软地。虽不敢辞。而内自循省。亦岂无自招者耶。盖自贼鑴力攻退,栗诸老先生。上以及于朱夫子。肆然无所忌惮。至将尽除夫子注释。而自立己说。遽然为成书。以示于众。一时靡然从之。以为胜于朱子。转相传录。犹恐不及。其不然者。例遭罪斥。愚不量其力之不足。妄加抵排。而并及其党助者。言多不中。以激众怒。虽曰乱贼之人。不必士师诛之。然龟山所讥一杯水救车薪之火者。不亦可笑之甚乎。其党助者既众。而势焰熏天。然后乃作大祸。而以愚为之首。虽困极海上。而顾其初则实出于为世道障横流。则九死而不悔矣。及鑴伏法之后。其平日尊崇之馀党。不敢言而敢怒。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89H 页
 而其怒丛于此汉。今日纷纷无足怪也。猥蒙知奖。略此陈闻。悚仄悚仄。
而其怒丛于此汉。今日纷纷无足怪也。猥蒙知奖。略此陈闻。悚仄悚仄。所论朱子论性说异同。前于宋上舍行。略呈瞽说矣。今闻尚未登彻。可讶可讶。兹者复蒙垂教。可见不措之盛心也。大抵朱子前后与人书及语类所记者。多有异同。盖或从天道说。或从人性说。或从生字说。或从静字说。故不能无异同。然言各有所当。须各随其所指而推究。则恐不至相妨矣。然其直解明道本意。则窃恐无如答严书也。此书亦全载于语类矣。今所与士元面论者甚多。晨昏之际。或能诠达其一二矣。然终未归一。则姑且置之。使之濯旧来新。不必求造次相合也。如何如何。
尤庵先生书(乙丑四月○此书自东莱传来。黔岩时为东莱府使。)
节届天中。缅惟静里起处珍毖。第未知见看何书。必有日新之功。而远不与相观之列。是用恨叹也。此衰病日加。虚过百年。正犯邵先生大戒。奈何奈何。日前贤胤归所禀继善说。不至大悖否。大抵读书。不密不疏。看来看去。意味深长。若被缠绕。解脱不得。则反无理义悦心之意矣。莱令此与家甥有秦晋之约。从此益成契谊。则弊门之幸也。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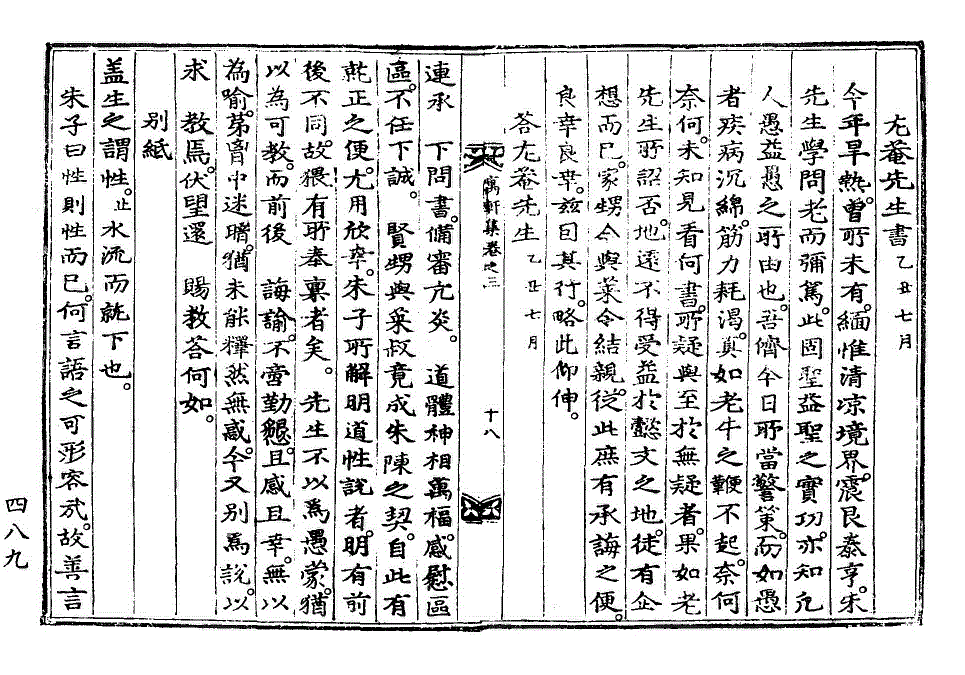 尤庵先生书(乙丑七月)
尤庵先生书(乙丑七月)今年旱热。曾所未有。缅惟清凉境界。震艮泰亨。朱先生学问老而弥笃。此固圣益圣之实功。亦知凡人愚益愚之所由也。吾侪今日所当警策。而如愚者疾病沈绵。筋力耗渴。真如老牛之鞭不起。奈何奈何。未知见看何书。所疑与至于无疑者。果如老先生所诏否。地远不得受益于懿文之地。徒有企想而已。家甥今与莱令结亲。从此庶有承诲之便。良幸良幸。兹因其行。略此仰伸。
答尤庵先生(乙丑七月)
连承 下问书。备审亢炎。 道体神相万福。感慰区区。不任下诚。 贤甥与莱叔竟成朱陈之契。自此有就正之便。尤用欣幸。朱子所解明道性说者。明有前后不同。故猥有所奉禀者矣。 先生不以为愚蒙。犹以为可教。而前后 诲谕。不啻勤恳。且感且幸。无以为喻。第胸中迷暗。犹未能释然无惑。今又别为说。以求 教焉。伏望还 赐教答何如。
别纸
盖生之谓性。(止)水流而就下也。
朱子曰性则性而已。何言语之可形容哉。故善言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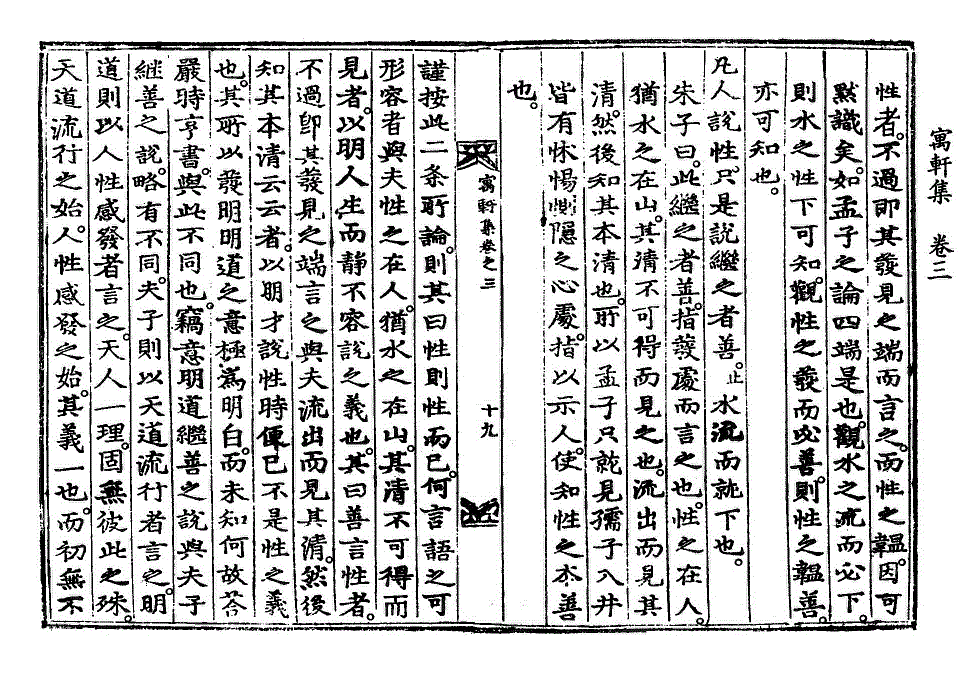 性者。不过即其发见之端而言之。而性之韫。因可默识矣。如孟子之论四端是也。观水之流而必下。则水之性下可知。观性之发而必善。则性之韫善。亦可知也。
性者。不过即其发见之端而言之。而性之韫。因可默识矣。如孟子之论四端是也。观水之流而必下。则水之性下可知。观性之发而必善。则性之韫善。亦可知也。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止)水流而就下也。
朱子曰。此继之者善。指发处而言之也。性之在人。犹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见之也。流出而见其清。然后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处。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也。
谨按此二条所论。则其曰性则性而已。何言语之可形容者与。夫性之在人。犹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见者。以明人生而静不容说之义也。其曰善言性者。不过即其发见之端言之与夫流出而见其清。然后知其本清云云者。以明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之义也。其所以发明明道之意极为明白。而未知何故答严时亨书。与此不同也。窃意明道继善之说与夫子继善之说。略有不同。夫子则以天道流行者言之。明道则以人性感发者言之。天人一理。固无彼此之殊。天道流行之始。人性感发之始。其义一也。而初无不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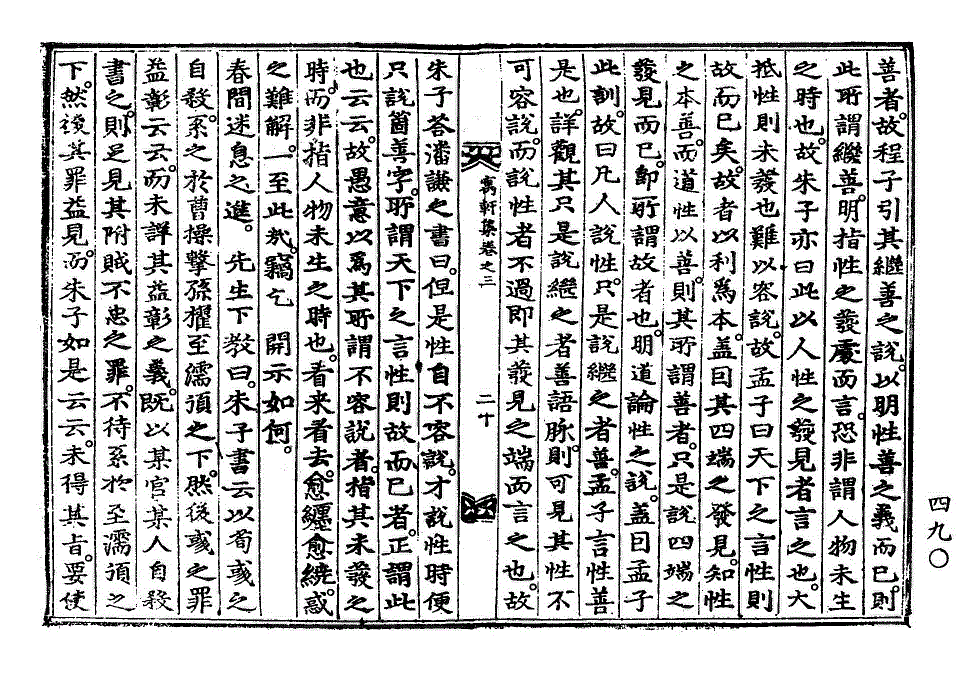 善者。故程子引其继善之说。以明性善之义而已。则此所谓继善。明指性之发处而言。恐非谓人物未生之时也。故朱子亦曰此以人性之发见者言之也。大抵性则未发也难以容说。故孟子曰天下之言性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盖因其四端之发见。知性之本善。而道性以善。则其所谓善者。只是说四端之发见而已。即所谓故者也。明道论性之说。盖因孟子此训。故曰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孟子言性善是也。详观其只是说继之者善语脉。则可见其性不可容说。而说性者不过即其发见之端而言之也。故朱子答潘谦之书曰。但是性自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只说个善字。所谓天下之言性则故而已者。正谓此也云云。故愚意以为其所谓不容说者。指其未发之时。而非指人物未生之时也。看来看去。愈缠愈绕。惑之难解。一至此哉。窃乞 开示如何。
善者。故程子引其继善之说。以明性善之义而已。则此所谓继善。明指性之发处而言。恐非谓人物未生之时也。故朱子亦曰此以人性之发见者言之也。大抵性则未发也难以容说。故孟子曰天下之言性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盖因其四端之发见。知性之本善。而道性以善。则其所谓善者。只是说四端之发见而已。即所谓故者也。明道论性之说。盖因孟子此训。故曰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孟子言性善是也。详观其只是说继之者善语脉。则可见其性不可容说。而说性者不过即其发见之端而言之也。故朱子答潘谦之书曰。但是性自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只说个善字。所谓天下之言性则故而已者。正谓此也云云。故愚意以为其所谓不容说者。指其未发之时。而非指人物未生之时也。看来看去。愈缠愈绕。惑之难解。一至此哉。窃乞 开示如何。春间迷息之进。 先生下教曰。朱子书云以荀彧之自杀。系之于曹操击孙权至濡须之下。然后彧之罪益彰云云。而未详其益彰之义。既以某官某人自杀书之。则足见其附贼不忠之罪。不待系于至濡须之下。然后其罪益见。而朱子如是云云。未得其旨。要使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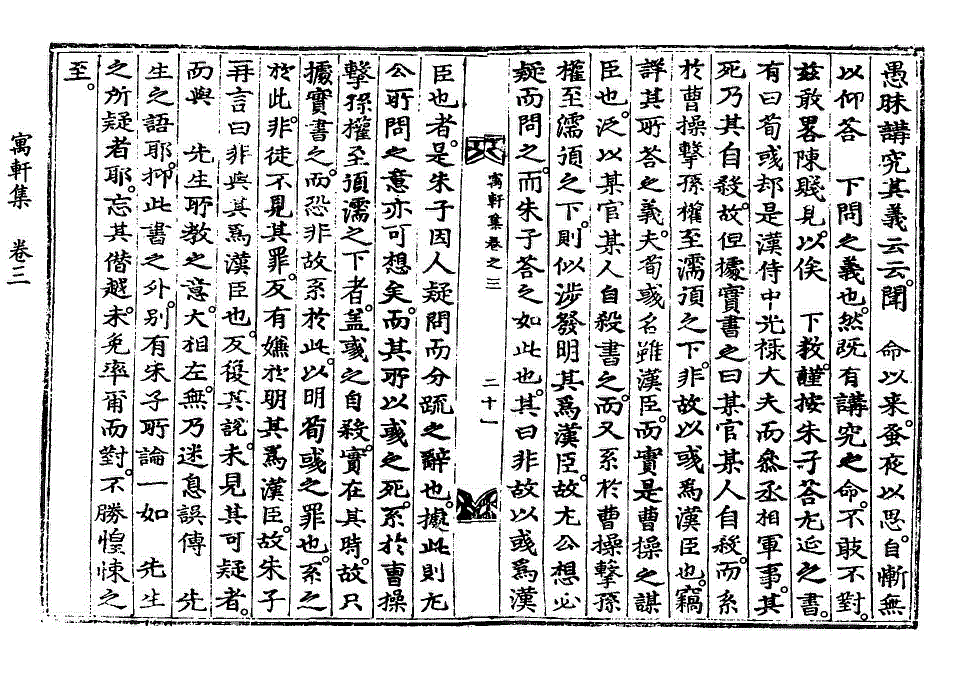 愚昧讲究其义云云。闻 命以来。蚤夜以思。自惭无以仰答 下问之义也。然既有讲究之命。不敢不对。兹敢略陈贱见。以俟 下教。谨按朱子答尤延之书。有曰荀彧却是汉侍中光禄大夫而参丞相军事。其死乃其自杀。故但据实书之曰某官某人自杀。而系于曹操击孙权至濡须之下。非故以彧为汉臣也。窃详其所答之义。夫荀彧名虽汉臣。而实是曹操之谋臣也。泛以某官某人自杀书之。而又系于曹操击孙权至濡须之下。则似涉发明其为汉臣。故尤公想必疑而问之。而朱子答之如此也。其曰非故以彧为汉臣也者。是朱子因人疑问而分疏之辞也。据此则尤公所问之意亦可想矣。而其所以彧之死。系于曹操击孙权至濡须之下者。盖彧之自杀。实在其时。故只据实书之。而恐非故系于此。以明荀彧之罪也。系之于此。非徒不见其罪。反有嫌于明其为汉臣。故朱子再言曰非与其为汉臣也。反复其说。未见其可疑者。而与 先生所教之意。大相左。无乃迷息误传 先生之语耶。抑此书之外。别有朱子所论一如 先生之所疑者耶。忘其僭越。未免率尔而对。不胜惶悚之至。
愚昧讲究其义云云。闻 命以来。蚤夜以思。自惭无以仰答 下问之义也。然既有讲究之命。不敢不对。兹敢略陈贱见。以俟 下教。谨按朱子答尤延之书。有曰荀彧却是汉侍中光禄大夫而参丞相军事。其死乃其自杀。故但据实书之曰某官某人自杀。而系于曹操击孙权至濡须之下。非故以彧为汉臣也。窃详其所答之义。夫荀彧名虽汉臣。而实是曹操之谋臣也。泛以某官某人自杀书之。而又系于曹操击孙权至濡须之下。则似涉发明其为汉臣。故尤公想必疑而问之。而朱子答之如此也。其曰非故以彧为汉臣也者。是朱子因人疑问而分疏之辞也。据此则尤公所问之意亦可想矣。而其所以彧之死。系于曹操击孙权至濡须之下者。盖彧之自杀。实在其时。故只据实书之。而恐非故系于此。以明荀彧之罪也。系之于此。非徒不见其罪。反有嫌于明其为汉臣。故朱子再言曰非与其为汉臣也。反复其说。未见其可疑者。而与 先生所教之意。大相左。无乃迷息误传 先生之语耶。抑此书之外。别有朱子所论一如 先生之所疑者耶。忘其僭越。未免率尔而对。不胜惶悚之至。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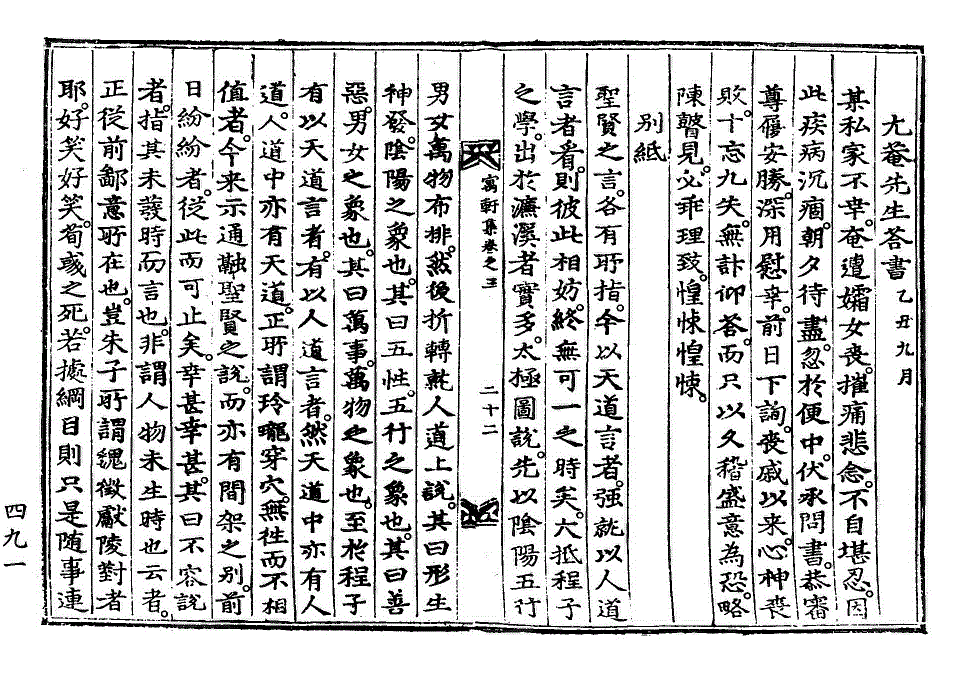 尤庵先生答书(乙丑九月)
尤庵先生答书(乙丑九月)某私家不幸。奄遭孀女丧。摧痛悲念。不自堪忍。因此疾病沈痼。朝夕待尽。忽于便中。伏承问书。恭审尊履安胜。深用慰幸。前日下询。丧戚以来。心神丧败。十忘九失。无计仰答。而只以久稽盛意为恐。略陈瞽见。必乖理致。惶悚惶悚。
别纸
圣贤之言。各有所指。今以天道言者。强就以人道言者看。则彼此相妨。终无可一之时矣。大抵程子之学。出于濂溪者实多。太极图说。先以阴阳五行男女万物布排。然后折转就人道上说。其曰形生神发。阴阳之象也。其曰五性。五行之象也。其曰善恶。男女之象也。其曰万事。万物之象也。至于程子有以天道言者。有以人道言者。然天道中亦有人道。人道中亦有天道。正所谓玲珑穿穴。无往而不相值者。今来示通融圣贤之说。而亦有间架之别。前日纷纷者。从此而可止矣。幸甚幸甚。其曰不容说者。指其未发时而言也。非谓人物未生时也云者。正从前鄙意所在也。岂朱子所谓魏徵献陵对者耶。好笑好笑。荀彧之死。若据纲目则只是随事连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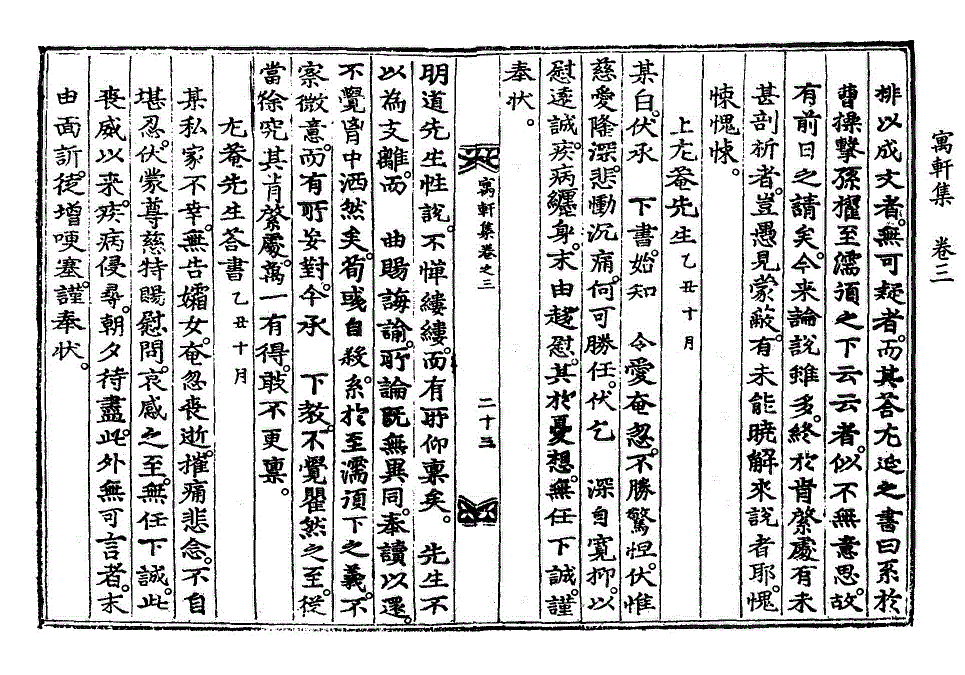 排以成文者。无可疑者。而其答尤延之书曰系于曹操击孙权至濡须之下云云者。似不无意思。故有前日之请矣。今来论说虽多。终于肯綮处有未甚剖析者。岂愚见蒙蔽。有未能晓解来说者耶。愧悚愧悚。
排以成文者。无可疑者。而其答尤延之书曰系于曹操击孙权至濡须之下云云者。似不无意思。故有前日之请矣。今来论说虽多。终于肯綮处有未甚剖析者。岂愚见蒙蔽。有未能晓解来说者耶。愧悚愧悚。上尤庵先生(乙丑十月)
某白。伏承 下书。始知 令爱奄忽。不胜惊怛。伏惟慈爱隆深。悲恸沈痛。何可胜任。伏乞 深自宽抑。以慰远诚。疾病缠身。末由趋慰。其于忧想。无任下诚。谨奉状。
明道先生性说。不惮缕缕。而有所仰禀矣。 先生不以为支离。而 曲赐诲谕。所论既无异同。奉读以还。不觉胸中洒然矣。荀彧自杀。系于至濡须下之义。不察微意。而有所妄对。今承 下教。不觉瞿然之至。从当徐究其肯綮处。万一有得。敢不更禀。
尤庵先生答书(乙丑十月)
某私家不幸。无告孀女。奄忽丧逝。摧痛悲念。不自堪忍。伏蒙尊慈特赐慰问。哀感之至。无任下诚。此丧威以来。疾病侵寻。朝夕待尽。此外无可言者。末由面诉。徒增哽塞。谨奉状。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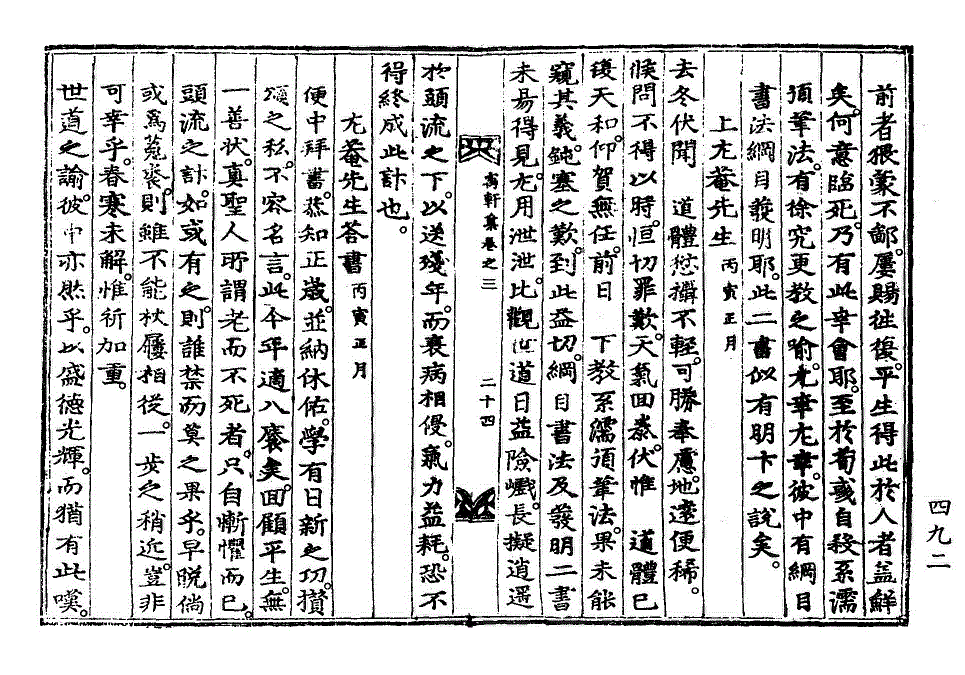 前者猥蒙不鄙。屡赐往复。平生得此于人者益鲜矣。何意临死。乃有此幸会耶。至于荀彧自杀系濡须笔法。有徐究更教之喻。尤幸尤幸。彼中有纲目书法纲目发明耶。此二书似有明卞之说矣。
前者猥蒙不鄙。屡赐往复。平生得此于人者益鲜矣。何意临死。乃有此幸会耶。至于荀彧自杀系濡须笔法。有徐究更教之喻。尤幸尤幸。彼中有纲目书法纲目发明耶。此二书似有明卞之说矣。上尤庵先生(丙寅正月)
去冬伏闻 道体愆摄不轻。可胜奉虑。地远便稀。 候问不得以时。恒切罪叹。天气回泰。伏惟 道体已复天和。仰贺无任。前日 下教系濡须笔法。果未能窥其义。钝塞之叹。到此益切。纲目书法及发明二书未易得见。尤用泄泄。比观世道日益险巇。长拟逍遥于头流之下。以送残年。而衰病相侵。气力益耗。恐不得终成此计也。
尤庵先生答书(丙寅正月)
便中拜书。恭知正岁。并纳休佑。学有日新之功。攒颂之私。不容名言。此今年适八帙矣。回顾平生。无一善状。真圣人所谓老而不死者。只自惭惧而已。头流之计。如或有之。则谁禁而莫之果乎。早晚倘或为莬裘。则虽不能杖屦相从。一步之稍近。岂非可幸乎。春寒未解。惟祈加重。
世道之谕。彼中亦然乎。以盛德光辉。而犹有此叹。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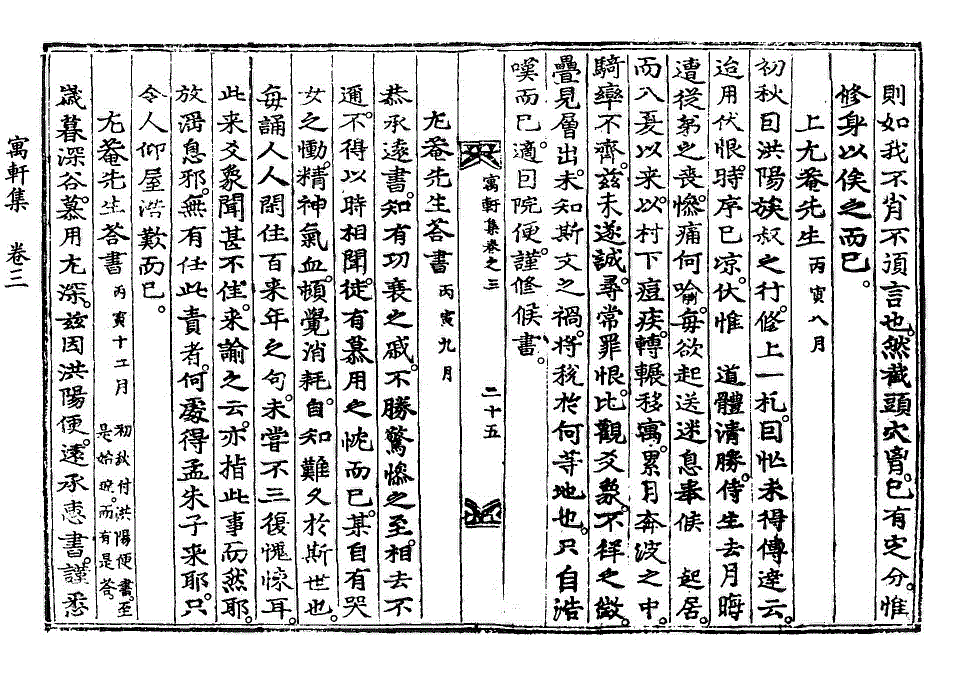 则如我不肖不须言也。然截头穴胸。已有定分。惟修身以俟之而已。
则如我不肖不须言也。然截头穴胸。已有定分。惟修身以俟之而已。上尤庵先生(丙寅八月)
初秋因洪阳族叔之行。修上一札。因忙未得传达云。迨用伏恨。时序已凉。伏惟 道体清胜。侍生去月晦遭从弟之丧。惨痛何喻。每欲起送迷息奉候 起居。而入夏以来。以村下痘疾。转辗移寓。累月奔波之中。骑率不齐。兹未遂诚。寻常罪恨。比观爻象。不祥之徵。叠见层出。未知斯文之祸。将税于何等地也。只自浩叹而已。适因院便。谨修候书。
尤庵先生答书(丙寅九月)
恭承远书。知有功衰之戚。不胜惊惨之至。相去不迩。不得以时相闻。徒有慕用之忱而已。某自有哭女之恸。精神气血。顿觉消耗。自知难久于斯世也。每诵人人闲住百来年之句。未尝不三复愧悚耳。此来爻象闻甚不佳。来谕之云。亦指此事而然耶。放淫息耶。无有任此责者。何处得孟朱子来耶。只令人仰屋浩叹而已。
尤庵先生答书(丙寅十二月○初秋付洪阳便书。至是始达。而有是答)
岁暮深谷。慕用尤深。兹因洪阳便。远承惠书。谨悉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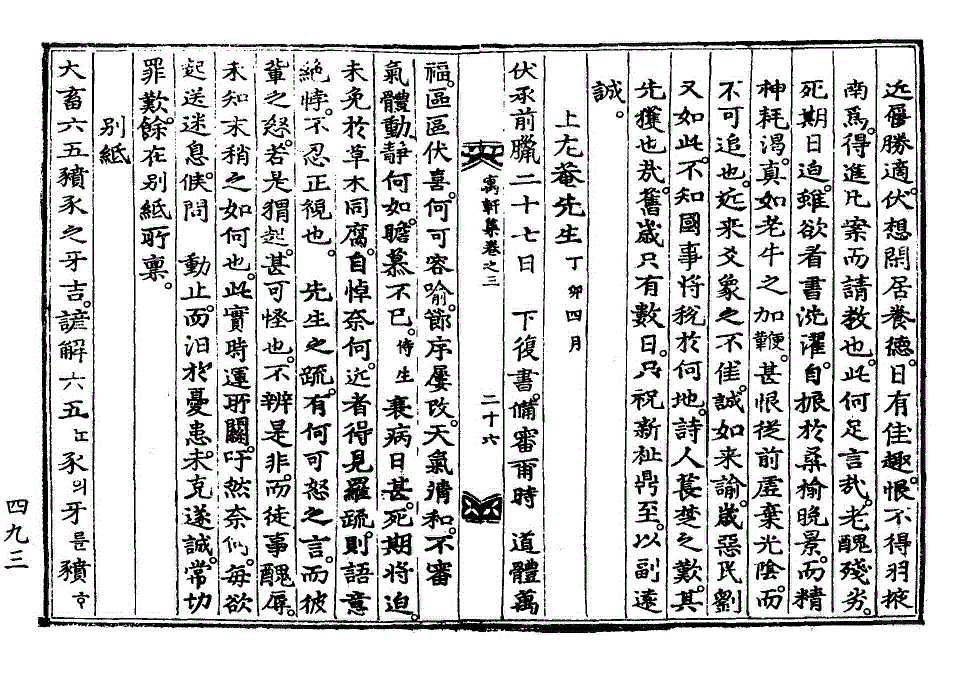 近履胜适。伏想闲居养德。日有佳趣。恨不得羽掖南为。得进几案而请教也。此何足言哉。老丑残劣。死期日迫。虽欲看书洗濯。自振于桑榆晚景。而精神耗渴。真如老牛之加鞭。甚恨从前虚弃光阴。而不可追也。近来爻象之不佳。诚如来谕。岁恶民刘又如此。不知国事将税于何地。诗人苌楚之叹。其先获也哉。旧岁只有数日。只祝新祉鼎至。以副远诚。
近履胜适。伏想闲居养德。日有佳趣。恨不得羽掖南为。得进几案而请教也。此何足言哉。老丑残劣。死期日迫。虽欲看书洗濯。自振于桑榆晚景。而精神耗渴。真如老牛之加鞭。甚恨从前虚弃光阴。而不可追也。近来爻象之不佳。诚如来谕。岁恶民刘又如此。不知国事将税于何地。诗人苌楚之叹。其先获也哉。旧岁只有数日。只祝新祉鼎至。以副远诚。上尤庵先生(丁卯四月)
伏承前腊二十七日。下复书。备审尔时 道体万福。区区伏喜。何可容喻。节序屡改。天气清和。不审 气体动静何如。瞻慕不已。侍生衰病日甚。死期将迫。未免于草木同腐。自悼奈何。近者得见罗疏。则语意绝悖。不忍正视也。 先生之疏。有何可怒之言。而彼辈之怒。若是猬起。甚可怪也。不辨是非。而徒事丑辱。未知末稍之如何也。此实时运所关。吁然奈何。每欲起送迷息。候问 动止。而汨于忧患。未克遂诚。常切罪叹。馀在别纸所禀。
别纸
大畜六五豮豕之牙吉。谚解六五()豕(의)牙(를)豮(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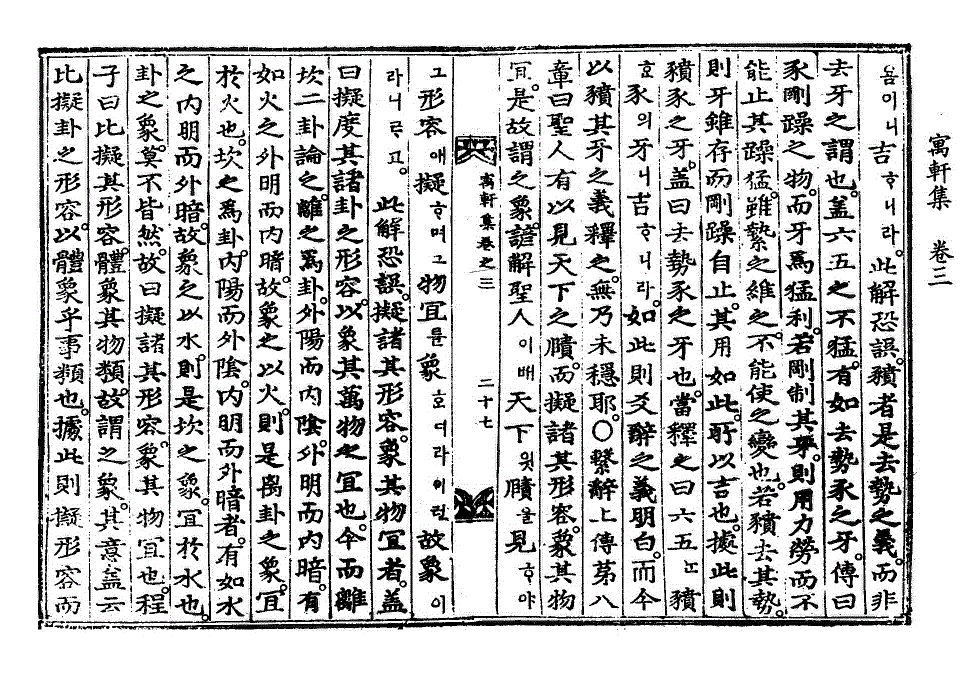 욤이니)吉(니라)。此解恐误。豮者是去势之义。而非去牙之谓也。盖六五之不猛。有如去势豕之牙。传曰豕刚躁之物。而牙为猛利。若刚制其牙。则用力劳而不能止其躁猛。虽絷之维之。不能使之变也。若豮去其势。则牙虽存而刚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据此则豮豕之牙。盖曰去势豕之牙也。当释之曰六五()豮()豕(의)牙(니)吉(니라)。如此则爻辞之义明白。而今以豮其牙之义释之。无乃未稳耶。○系辞上传第八章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谚解圣人(이배)天下(읫)赜(을)见(야그)形容(애)拟(며그)物宜(를)象(디라이런)故象(이라니고)。此解恐误。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者。盖曰拟度其诸卦之形容。以象其万物之宜也。今而离坎二卦论之。离之为卦。外阳而内阴。外明而内暗。有如火之外明而内暗。故象之以火。则是离卦之象。宜于火也。坎之为卦。内阳而外阴。内明而外暗者。有如水之内明而外暗。故象之以水。则是坎之象。宜于水也。卦之象。莫不皆然。故曰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也。程子曰比拟其形容。体象其物类。故谓之象。其意盖云比拟卦之形容。以体象乎事类也。据此则拟形容而
욤이니)吉(니라)。此解恐误。豮者是去势之义。而非去牙之谓也。盖六五之不猛。有如去势豕之牙。传曰豕刚躁之物。而牙为猛利。若刚制其牙。则用力劳而不能止其躁猛。虽絷之维之。不能使之变也。若豮去其势。则牙虽存而刚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据此则豮豕之牙。盖曰去势豕之牙也。当释之曰六五()豮()豕(의)牙(니)吉(니라)。如此则爻辞之义明白。而今以豮其牙之义释之。无乃未稳耶。○系辞上传第八章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谚解圣人(이배)天下(읫)赜(을)见(야그)形容(애)拟(며그)物宜(를)象(디라이런)故象(이라니고)。此解恐误。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者。盖曰拟度其诸卦之形容。以象其万物之宜也。今而离坎二卦论之。离之为卦。外阳而内阴。外明而内暗。有如火之外明而内暗。故象之以火。则是离卦之象。宜于火也。坎之为卦。内阳而外阴。内明而外暗者。有如水之内明而外暗。故象之以水。则是坎之象。宜于水也。卦之象。莫不皆然。故曰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也。程子曰比拟其形容。体象其物类。故谓之象。其意盖云比拟卦之形容。以体象乎事类也。据此则拟形容而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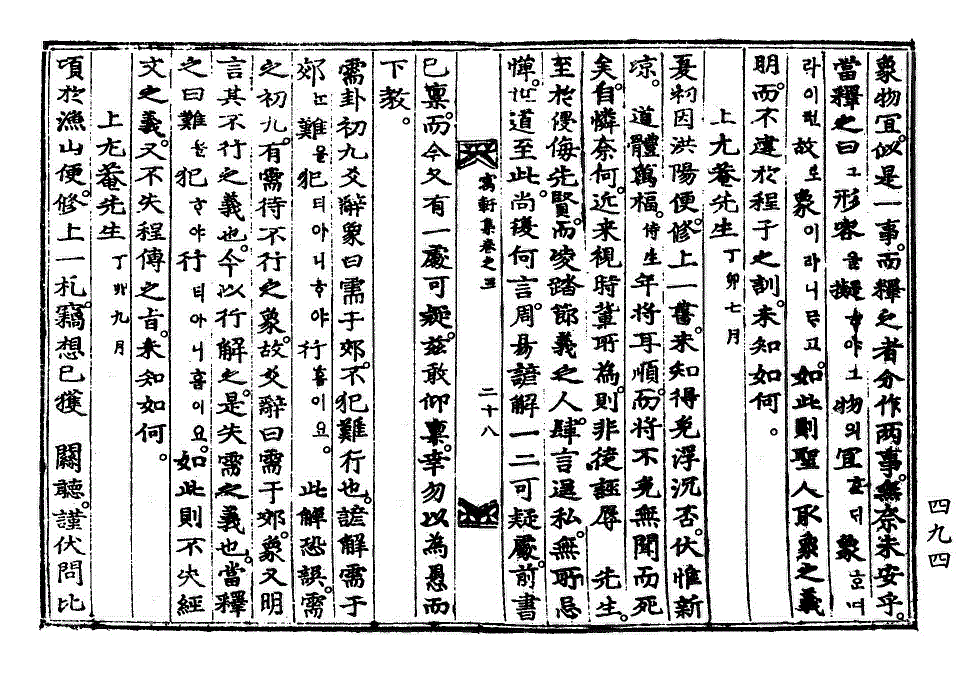 象物宜。似是一事。而释之者分作两事。无奈未安乎。当释之曰(그)形容(을)拟(야그)物(의)宜(偓)象(디라이런)故(로)象(이라니고)。如此则圣人取象之义明。而不违于程子之训。未知如何。
象物宜。似是一事。而释之者分作两事。无奈未安乎。当释之曰(그)形容(을)拟(야그)物(의)宜(偓)象(디라이런)故(로)象(이라니고)。如此则圣人取象之义明。而不违于程子之训。未知如何。上尤庵先生(丁卯七月)
夏初因洪阳便。修上一书。未知得免浮沈否。伏惟新凉。 道体万福。侍生年将耳顺。而将不免无闻而死矣。自怜奈何。近来视时辈所为。则非徒诬辱 先生。至于侵侮先贤。而凌踏节义之人。肆言逞私。无所忌惮。世道至此。尚复何言。周易谚解一二可疑处。前书已禀。而今又有一处可疑。兹敢仰禀。幸勿以为愚而下教。
需卦初九爻辞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谚解需于郊()难(을)犯(티아니야)行(흠이요)。 此解恐误。需之初九。有需待不行之象。故爻辞曰需于郊。象又明言其不行之义也。今以行解之。是失需之义也。当释之曰难(을)犯(야)行(티아니홈이요)。如此则不失经文之义。又不失程传之旨。未知如何。
上尤庵先生(丁卯九月)
顷于渔山便。修上一札。窃想已获 关听。谨伏问比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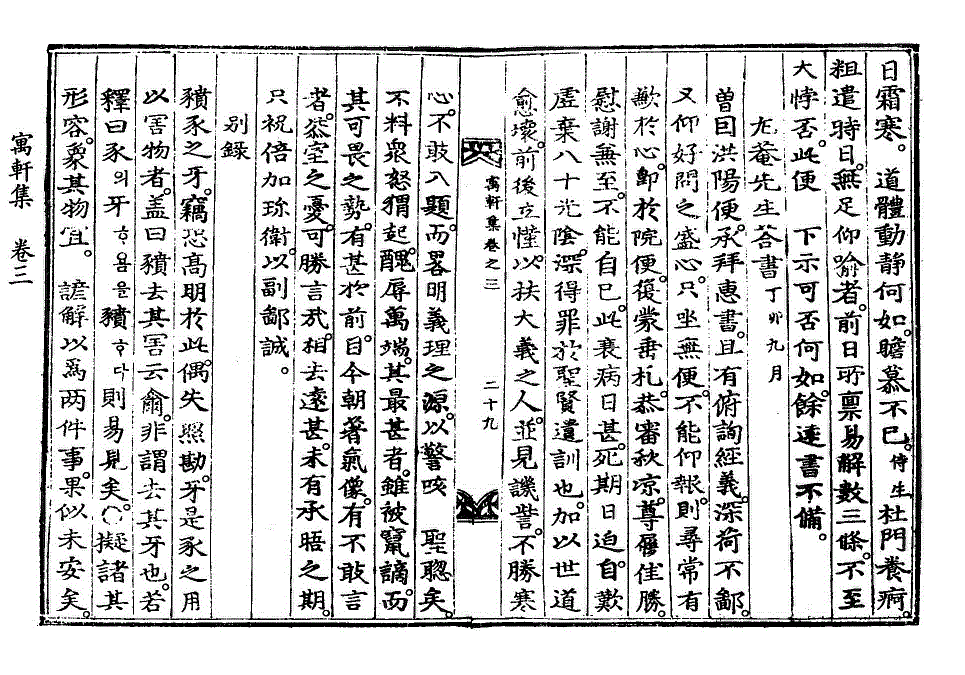 日霜寒。 道体动静何如。瞻慕不已。侍生杜门养痾。粗遣时日。无足仰喻者。前日所禀易解数三条。不至大悖否。此便 下示可否何如。馀远书不备。
日霜寒。 道体动静何如。瞻慕不已。侍生杜门养痾。粗遣时日。无足仰喻者。前日所禀易解数三条。不至大悖否。此便 下示可否何如。馀远书不备。尤庵先生答书(丁卯九月)
曾因洪阳便。承拜惠书。且有俯询经义。深荷不鄙。又仰好问之盛心。只坐无便。不能仰报。则寻常有歉于心。即于院便。复蒙垂札。恭审秋凉。尊履佳胜。慰谢兼至。不能自已。此衰病日甚。死期日迫。自叹虚弃八十光阴。深得罪于圣贤遗训也。加以世道愈坏。前后立慬。以扶大义之人。并见讥訾。不胜寒心。不敢入题。而略明义理之源。以警咳 圣聪矣。不料众怒猬起。丑辱万端。其最甚者。虽被窜谪。而其可畏之势。有甚于前。目今朝著气像。有不敢言者。漆室之忧。可胜言哉。相去远甚。未有承晤之期。只祝倍加珍卫。以副鄙诚。
别录
豮豕之牙。窃恐高明于此。偶失照勘。牙是豕之用以害物者。盖曰豮去其害云尔。非谓去其牙也。若释曰豕(의)牙(욤을)豮(다)则易见矣。○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 谚解以为两件事。果似未安矣。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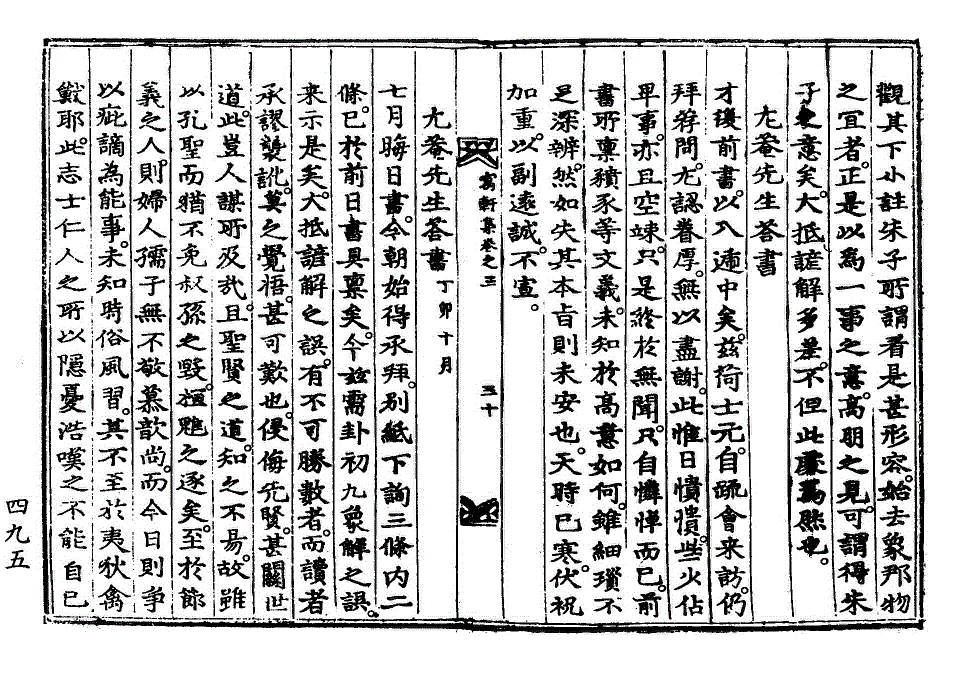 观其下小注朱子所谓看是甚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者。正是以为一事之意。高明之见。可谓得朱子之意矣。大抵谚解多差。不但此处为然也。
观其下小注朱子所谓看是甚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者。正是以为一事之意。高明之见。可谓得朱子之意矣。大抵谚解多差。不但此处为然也。尤庵先生答书
才复前书。以入递中矣。玆荷士元。自疏会来访。仍拜荐问。尤认眷厚。无以尽谢。此惟日愦愦。些少佔卑事。亦且空竦。只是终于无闻。只自怜悼而已。前书所禀豮豕等文义。未知于高意如何。虽细琐不足深辨。然如失其本旨则未安也。天时已寒。伏祝加重。以副远诚。不宣。
尤庵先生答书(丁卯十月)
七月晦日书。今朝始得承拜。别纸下询三条内二条。已于前日书具禀矣。今兹需卦初九象解之误。来示是矣。大抵谚解之误。有不可胜数者。而读者承谬袭讹。莫之觉悟。甚可叹也。侵侮先贤。甚关世道。此岂人谋所及哉。且圣贤之道。知之不易。故虽以孔圣而犹不免叔孙之毁。桓魋之逐矣。至于节义之人。则妇人孺子无不敬慕歆尚。而今日则争以疵谪为能事。未知时俗风习。其不至于夷狄禽兽耶。此志士仁人之所以隐忧浩叹之不能自已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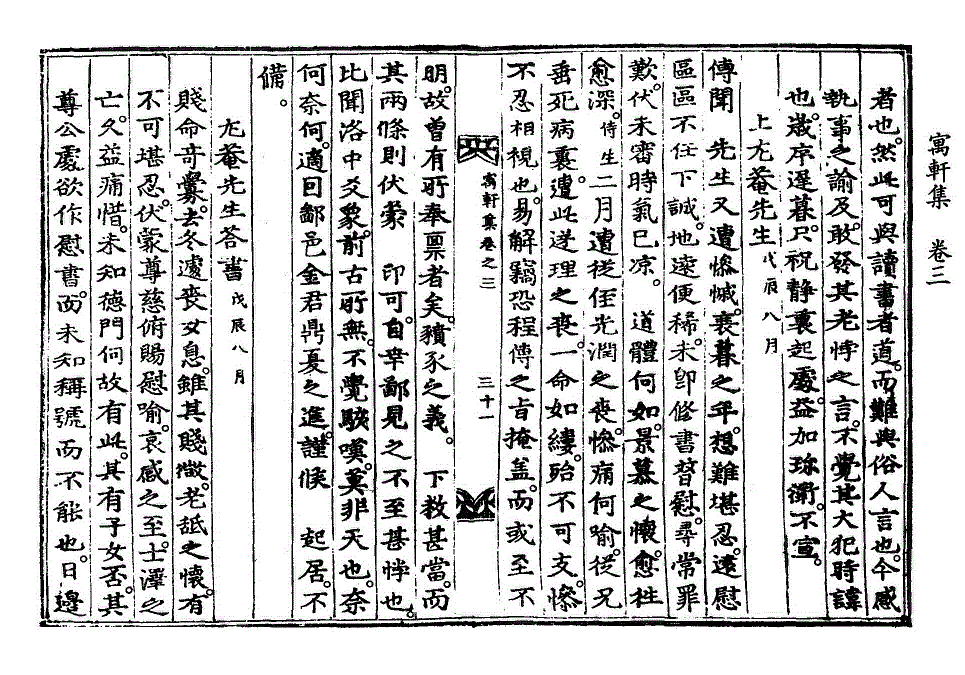 者也。然此可与读书者道。而难与俗人言也。今感执事之谕及。敢发其老悖之言。不觉其大犯时讳也。岁序迟暮。只祝静里起处。益加珍卫。不宣。
者也。然此可与读书者道。而难与俗人言也。今感执事之谕及。敢发其老悖之言。不觉其大犯时讳也。岁序迟暮。只祝静里起处。益加珍卫。不宣。上尤庵先生(戊辰八月)
传闻 先生又遭惨戚。衰暮之年。想难堪忍。远慰区区不任下诚。地远便稀。未即修书替慰。寻常罪叹。伏未审时气已凉。 道体何如。景慕之怀。愈往愈深。侍生二月遭从侄光润之丧。惨痛何喻。从兄垂死病里。遭此逆理之丧。一命如缕。殆不可支。惨不忍相视也。易解窃恐程传之旨掩盖。而或至不明。故曾有所奉禀者矣。豮豕之义。 下教甚当。而其两条则伏蒙 印可。自幸鄙见之不至甚悖也。比闻洛中爻象。前古所无。不觉骇叹。莫非天也。奈何奈何。适因鄙邑金君鼎夏之进。谨候 起居。不备。
尤庵先生答书(戊辰八月)
贱命奇衅。去冬遽丧女息。虽其贱微。老舐之怀。有不可堪忍。伏蒙尊慈俯赐慰喻。哀感之至。士泽之亡。久益痛惜。未知德门何故有此。其有子女否。其尊公处欲作慰书。而未知称号而不能也。日边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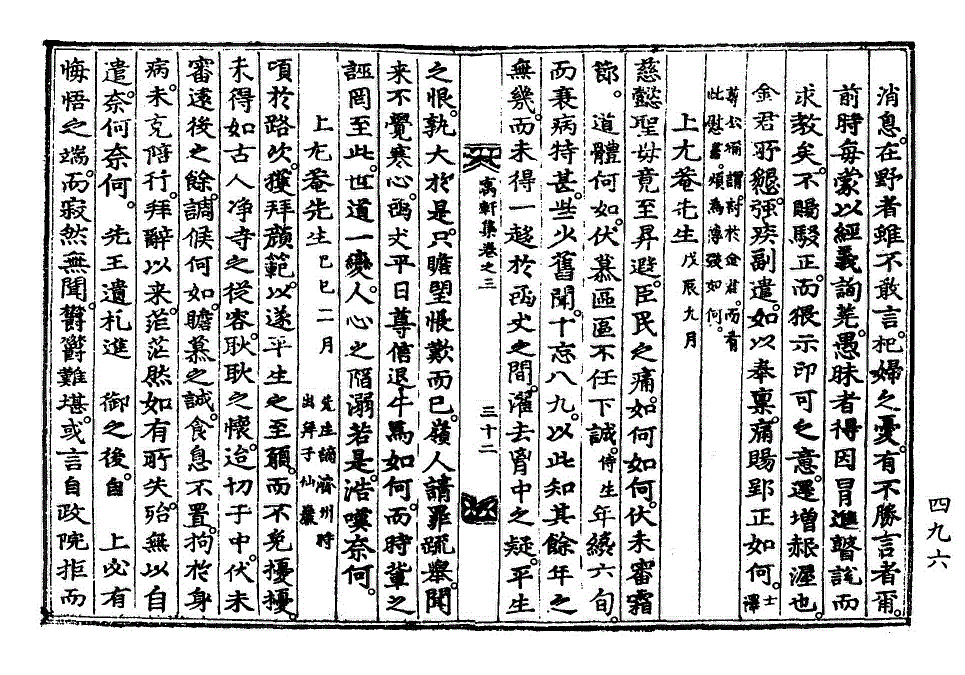 消息。在野者虽不敢言。杞妇之忧。有不胜言者尔。前时每蒙以经义询荛。愚昧者得因冒进瞽说而求教矣。不赐驳正。而猥示印可之意。还增赧渥也。金君所恳。强疾副遣。如以奉禀。痛赐郢正如何。(士泽尊公称谓。讨于金君。而有此慰书。烦为传致如何。)
消息。在野者虽不敢言。杞妇之忧。有不胜言者尔。前时每蒙以经义询荛。愚昧者得因冒进瞽说而求教矣。不赐驳正。而猥示印可之意。还增赧渥也。金君所恳。强疾副遣。如以奉禀。痛赐郢正如何。(士泽尊公称谓。讨于金君。而有此慰书。烦为传致如何。)上尤庵先生(戊辰九月)
慈懿圣母竟至升遐。臣民之痛。如何如何。伏未审霜节。 道体何如。伏慕区区不任下诚。侍生年才六旬。而衰病特甚。些少旧闻。十忘八九。以此知其馀年之无几。而未得一趋于函丈之间。濯去胸中之疑。平生之恨。孰大于是。只瞻望怅叹而已。岭人请罪疏举。闻来不觉寒心。函丈平日尊信退,牛为如何。而时辈之诬罔至此。世道一变。人心之陷溺若是。浩叹奈何。
上尤庵先生(己巳二月○先生谪济州时出拜于仙岩)
顷于路次。获拜颜范。以遂平生之至愿。而不免扰扰。未得如古人净寺之从容。耿耿之怀。迨切于中。伏未审远役之馀。调候何如。瞻慕之诚。食息不置。拘于身病。未克陪行。拜辞以来。茫茫然如有所失。殆无以自遣。奈何奈何。 先王遗札进 御之后。自 上必有悔悟之端。而寂然无闻。郁郁难堪。或言自政院拒而
寓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4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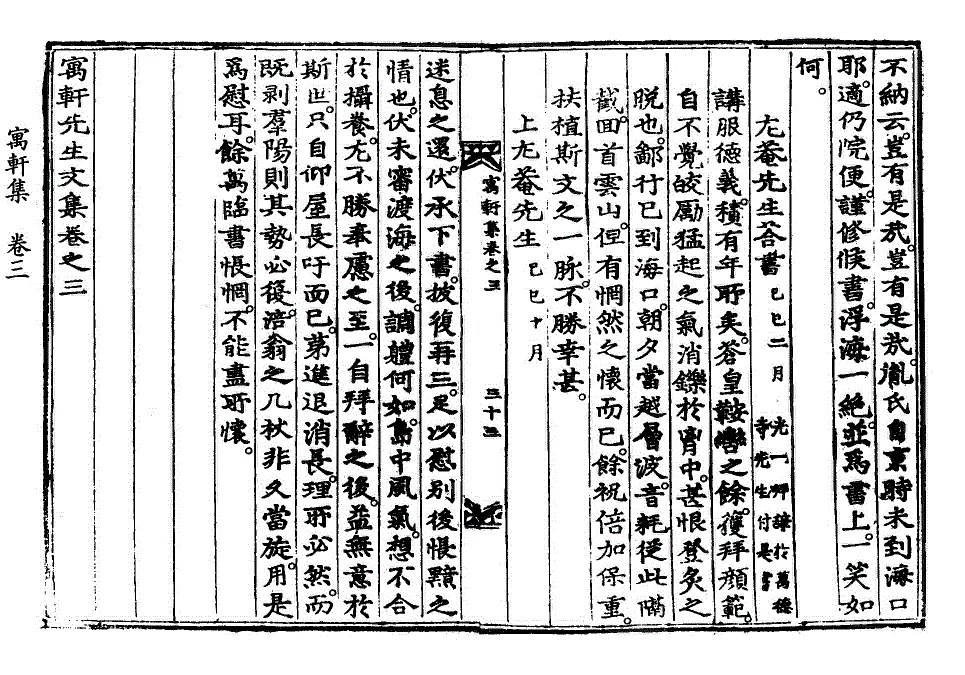 不纳云。岂有是哉。岂有是哉。胤氏自京时未到海口耶。适仍院便。谨修候书。浮海一绝。并为书上。一笑如何。
不纳云。岂有是哉。岂有是哉。胤氏自京时未到海口耶。适仍院便。谨修候书。浮海一绝。并为书上。一笑如何。尤庵先生答书(己巳二月○光一拜辞于万德寺先生付是书)
讲服德义。积有年所矣。苍皇鞍辔之馀。获拜颜范。自不觉皎励猛起之气消铄于胸中。甚恨登炙之晚也。鄙行已到海口。朝夕当越层波。音耗从此隔截。回首云山。但有惘然之怀而已。馀祝倍加保重。枎植斯文之一脉。不胜幸甚。
上尤庵先生(己巳十月)
迷息之还。伏承下书。披复再三。足以慰别后怅黯之情也。伏未审渡海之后。调体何如。岛中风气。想不合于摄养。尤不胜奉虑之至。一自拜辞之后。益无意于斯世。只自仰屋长吁而已。第进退消长。理所必然。而既剥群阳则其势必复。涪翁之几杖非久当旋。用是为慰耳。馀万临书怅惘。不能尽所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