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 第 x 页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诗文集总名曰合刊韶濩堂集○花开金泽荣于霖著)
序
序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 第 2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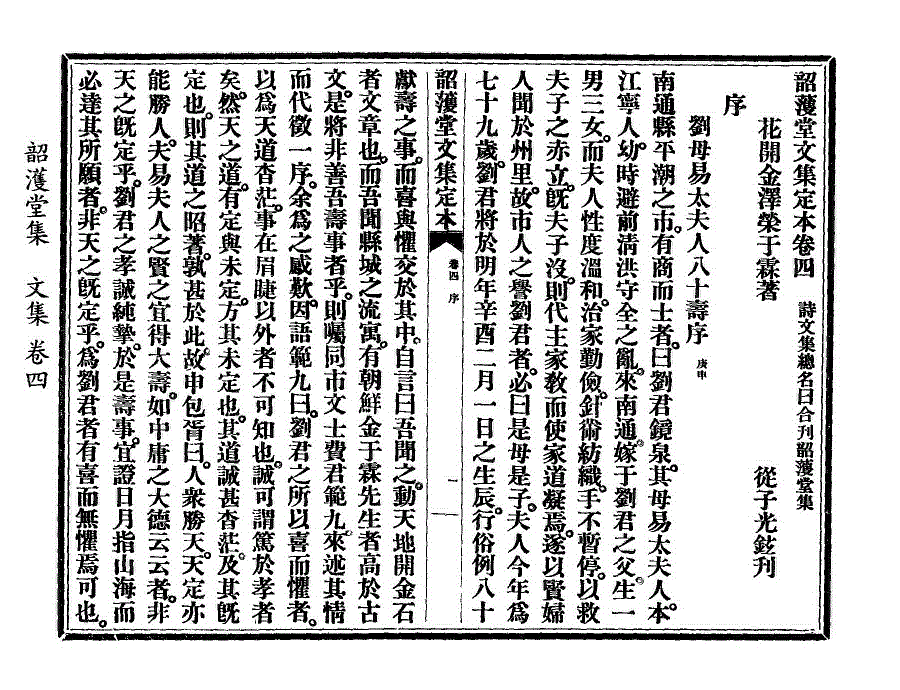 刘母易太夫人八十寿序(庚申)
刘母易太夫人八十寿序(庚申)南通县平潮之市。有商而士者。曰刘君镜泉。其母易太夫人。本江宁人。幼时避前清洪守全之乱。来南通。嫁于刘君之父。生一男三女。而夫人性度温和。治家勤俭。针黹纺织。手不暂停。以救夫子之赤立。既夫子没。则代主家教而使家道凝焉。遂以贤妇人闻于州里。故市人之誉刘君者。必曰是母是子。夫人今年为七十九岁。刘君将于明年辛酉二月一日之生辰。行俗例八十献寿之事。而喜与惧交于其中。自言曰吾闻之。动天地开金石者文章也。而吾闻县城之流寓。有朝鲜金于霖先生者高于古文。是将非善吾寿事者乎。则嘱同市文士费君范九。来述其情而代徵一序。余为之感叹。因语范九曰。刘君之所以喜而惧者。以为天道杳茫。事在眉睫以外者不可知也。诚可谓笃于孝者矣。然天之道。有定与未定。方其未定也。其道诚甚杳茫。及其既定也。则其道之昭著。孰甚于此。故申包胥曰。人众胜天。天定亦能胜人。夫易夫人之贤之宜得大寿。如中庸之大德云云者。非天之既定乎。刘君之孝诚纯挚。于是寿事。宜證日月指山海而必达其所愿者。非天之既定乎。为刘君者有喜而无惧焉可也。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 第 2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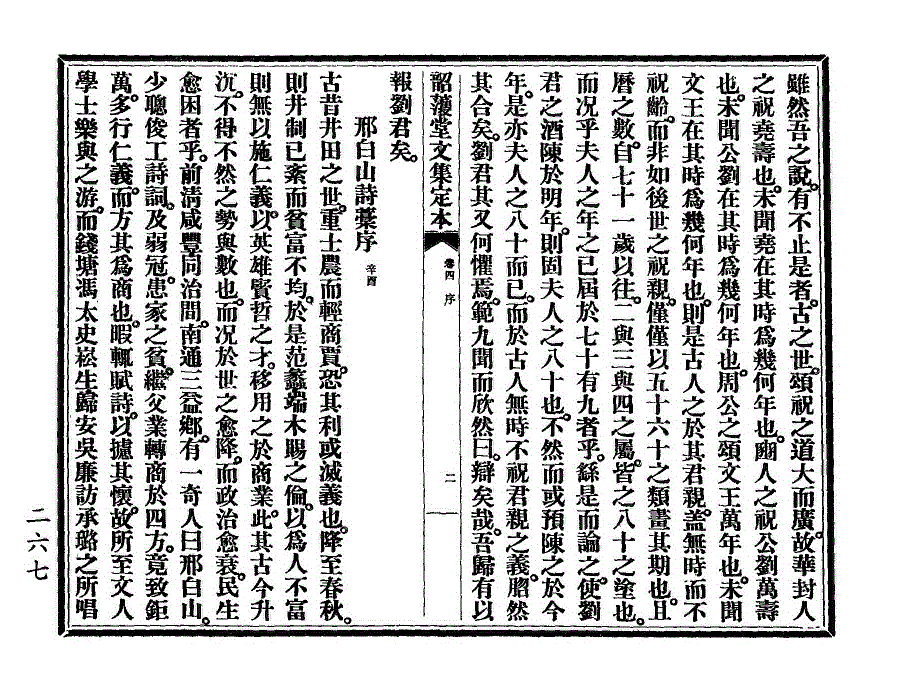 虽然吾之说。有不止是者。古之世。颂祝之道大而广。故华封人之祝尧寿也。未闻尧在其时为几何年也。豳人之祝公刘万寿也。未闻公刘在其时为几何年也。周公之颂文王万年也。未闻文王在其时为几何年也。则是古人之于其君亲。盖无时而不祝龄。而非如后世之祝亲。仅仅以五十六十之类画其期也。且历之数。自七十一岁以往。二与三与四之属。皆之八十之涂也。而况乎夫人之年之已届于七十有九者乎。繇是而论之。使刘君之酒陈于明年。则固夫人之八十也。不然而或预陈之于今年。是亦夫人之八十而已。而于古人无时不祝君亲之义。吻然其合矣。刘君其又何惧焉。范九闻而欣然曰。辩矣哉。吾归有以报刘君矣。
虽然吾之说。有不止是者。古之世。颂祝之道大而广。故华封人之祝尧寿也。未闻尧在其时为几何年也。豳人之祝公刘万寿也。未闻公刘在其时为几何年也。周公之颂文王万年也。未闻文王在其时为几何年也。则是古人之于其君亲。盖无时而不祝龄。而非如后世之祝亲。仅仅以五十六十之类画其期也。且历之数。自七十一岁以往。二与三与四之属。皆之八十之涂也。而况乎夫人之年之已届于七十有九者乎。繇是而论之。使刘君之酒陈于明年。则固夫人之八十也。不然而或预陈之于今年。是亦夫人之八十而已。而于古人无时不祝君亲之义。吻然其合矣。刘君其又何惧焉。范九闻而欣然曰。辩矣哉。吾归有以报刘君矣。邢白山诗藁序(辛酉)
古昔井田之世。重士农而轻商贾。恐其利或灭义也。降至春秋。则井制已紊而贫富不均。于是范蠡,端木赐之伦。以为人不富则无以施仁义。以英雄贤哲之才。移用之于商业。此其古今升沉。不得不然之势与数也。而况于世之愈降。而政治愈衰。民生愈困者乎。前清咸丰,同治间。南通三益乡。有一奇人曰邢白山。少聪俊工诗词。及弱冠。患家之贫。继父业转商于四方。竟致钜万。多行仁义。而方其为商也。暇辄赋诗。以摅其怀。故所至文人学士乐与之游。而钱塘冯太史崧生,归安吴廉访承璐之所唱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 第 2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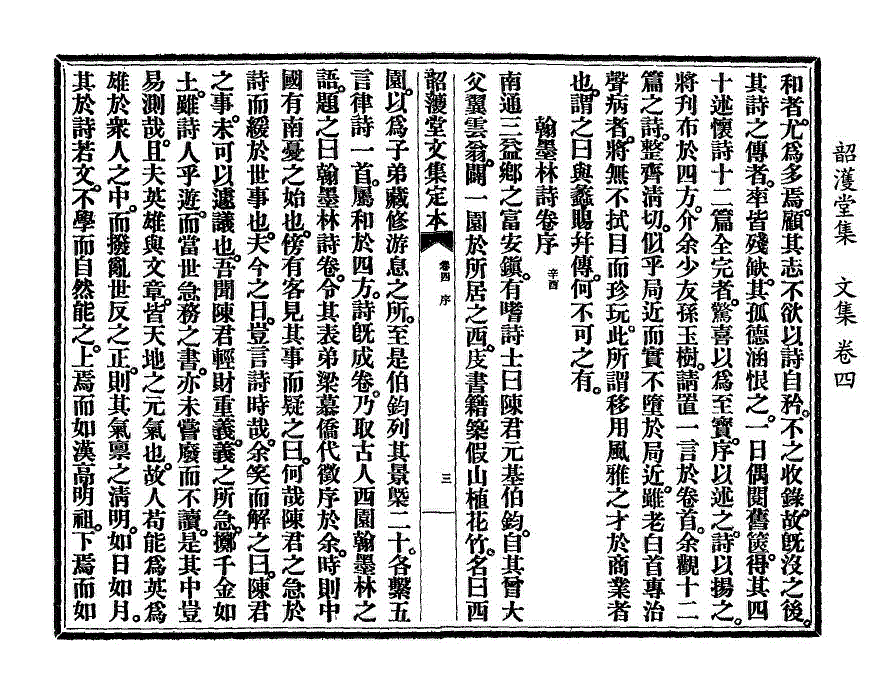 和者。尤为多焉。顾其志不欲以诗自矜。不之收录。故既没之后。其诗之传者。率皆残缺。其孤德涵恨之。一日偶阅旧箧。得其四十述怀诗十二篇全完者。惊喜以为至宝。序以述之。诗以扬之。将刊布于四方。介余少友孙玉树。请置一言于卷首。余观十二篇之诗。整齐清切。似乎局近而实不堕于局近。虽老白首专治声病者。将无不拭目而珍玩。此所谓移用风雅之才于商业者也。谓之曰与蠡,赐并传。何不可之有。
和者。尤为多焉。顾其志不欲以诗自矜。不之收录。故既没之后。其诗之传者。率皆残缺。其孤德涵恨之。一日偶阅旧箧。得其四十述怀诗十二篇全完者。惊喜以为至宝。序以述之。诗以扬之。将刊布于四方。介余少友孙玉树。请置一言于卷首。余观十二篇之诗。整齐清切。似乎局近而实不堕于局近。虽老白首专治声病者。将无不拭目而珍玩。此所谓移用风雅之才于商业者也。谓之曰与蠡,赐并传。何不可之有。翰墨林诗卷序(辛酉)
南通三益乡之富安镇。有嗜诗士曰陈君元基伯钧。自其曾大父翼云翁。辟一园于所居之西。庋书籍筑假山植花竹。名曰西园。以为子弟藏修游息之所。至是伯钧列其景槩二十。各系五言律诗一首。属和于四方。诗既成卷。乃取古人西园翰墨林之语。题之曰翰墨林诗卷。令其表弟梁慕侨代徵序于余。时则中国有南忧之始也。傍有客见其事而疑之曰。何哉陈君之急于诗而缓于世事也。夫今之日。岂言诗时哉。余笑而解之曰。陈君之事。未可以遽议也。吾闻陈君轻财重义。义之所急。掷千金如土。虽诗人乎游。而当世急务之书。亦未尝废而不读。是其中岂易测哉。且夫英雄与文章。皆天地之元气也。故人苟能为英为雄于众人之中。而拨乱世反之正。则其气禀之清明。如日如月。其于诗若文。不学而自然能之。上焉而如汉高,明祖。下焉而如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 第 2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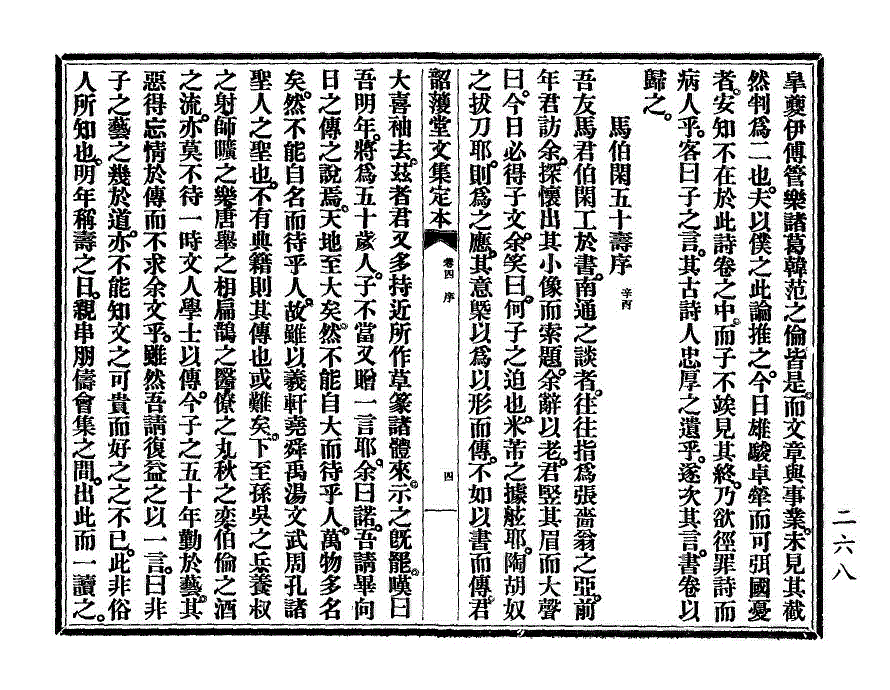 皋夔伊傅管乐诸葛韩范之伦皆是。而文章与事业。未见其截然判为二也。夫以仆之此论推之。今日雄骏卓荦而可弭国忧者。安知不在于此诗卷之中。而子不俟见其终。乃欲径罪诗而病人乎。客曰子之言。其古诗人忠厚之遗乎。遂次其言。书卷以归之。
皋夔伊傅管乐诸葛韩范之伦皆是。而文章与事业。未见其截然判为二也。夫以仆之此论推之。今日雄骏卓荦而可弭国忧者。安知不在于此诗卷之中。而子不俟见其终。乃欲径罪诗而病人乎。客曰子之言。其古诗人忠厚之遗乎。遂次其言。书卷以归之。马伯闲五十寿序(辛酉)
吾友马君伯闲工于书。南通之谈者。往往指为张啬翁之亚。前年君访余。探怀出其小像而索题。余辞以老。君竖其眉而大声曰。今日必得子文。余笑曰。何子之迫也。米芾之据舷耶。陶胡奴之拔刀耶。则为之应。其意槩以为以形而传。不如以书而传。君大喜袖去。兹者君又多持近所作草篆诸体来。示之既罢。叹曰吾明年。将为五十岁人。子不当又赠一言耶。余曰诺。吾请毕向日之传之说焉。天地至大矣。然不能自大而待乎人。万物多名矣。然不能自名而待乎人。故虽以羲轩尧舜禹汤文武周孔诸圣人之圣也。不有典籍则其传也或难矣。下至孙吴之兵,养叔之射,师旷之乐,唐举之相,扁鹊之医,僚之丸,秋之奕,伯伦之酒之流。亦莫不待一时文人学士以传。今子之五十年勤于艺。其恶得忘情于传而不求余文乎。虽然吾请复益之以一言。曰非子之艺之几于道。亦不能知文之可贵而好之之不已。此非俗人所知也。明年称寿之日。亲串朋俦会集之间。出此而一读之。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 第 269H 页
 其亦或为一日之乐。而无将老之叹矣乎。
其亦或为一日之乐。而无将老之叹矣乎。送王敬庵游枫岳序(辛酉)
王原初既贵而隐。矻矻读书。足不出里外者三十馀年。一朝闻枫岳之车路通。将往游之。走书以告。夫人戴夫(一作天)而不知天。履地而不知地耻也。故古之人于山岳川渎峰旒源流之远近多寡平险高下。必核书其实。如长江万里,泰山七十二峰,天台山四万八千丈之类者。不一而足。若是者或名为经。讵不重且大哉。吾邦人谈枫岳曰。其峰一万二千。为天下第一名山。此何说也。夫峰也者。山耑之大耸特立者。而非寻常嵁岩之类也。彼所谓一万二千者。指寻常嵁岩则可矣。若曰峰也。则尽大块八万里之山之峰而数之。且不能充其算。而况枫岳一百六十里之山者乎。夫枫岳之为山。有数十其峰。而怪奇谲诡。幽遐杳冥之观多焉。浮屠人之家其中者。尝以彼书所言昙无竭一万二千身之变幻者。举为山峰之数以夸之。彼浮屠者。既外人伦。安问地理。所以其说之荒谬至于如此。而庸人俗士之游于是者。目眩心醉于怪奇之观。遂以靡然从之。一唱万和。虽尔雅君子者。时或斥其荒谬。而一齐之言。无以当众楚之咻。可胜慨哉。大抵吾邦名山。第其等次。则天磨为最。其次为枫岳,俗离,妙香何也。彼枫岳以下诸山。皆在幽僻之区。而其状止于清奇。若天磨则处于名都大邑繁华之地。而兼有壮雄清奇之观。其壮雄清奇者。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 第 2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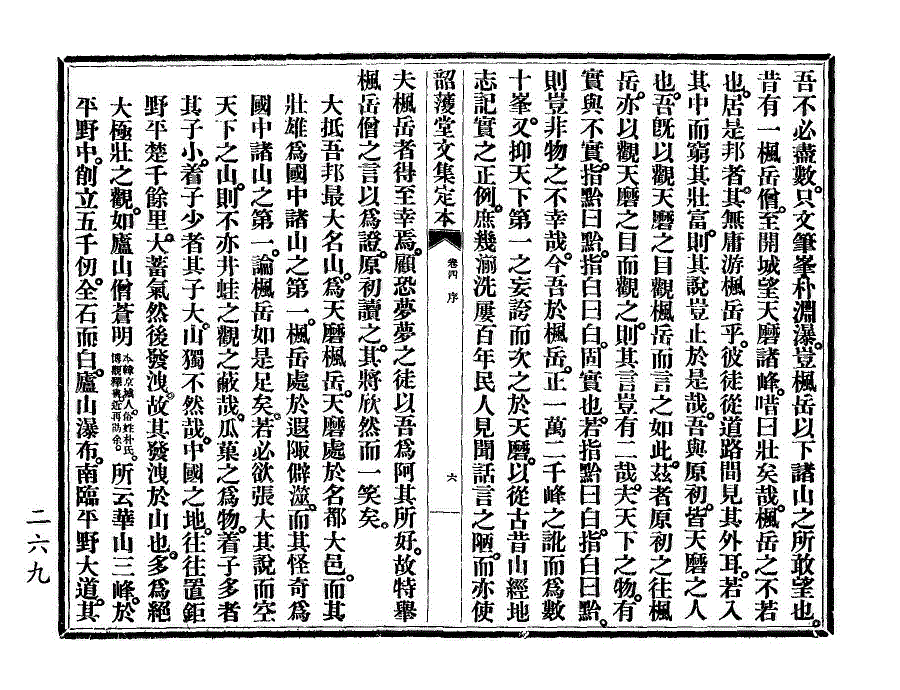 吾不必尽数。只文笔峰,朴渊瀑。岂枫岳以下诸山之所敢望也。昔有一枫岳僧。至开城望天磨诸峰。唶曰壮矣哉。枫岳之不若也。居是邦者。其无庸游枫岳乎。彼徒从道路间见其外耳。若入其中而穷其壮富。则其说岂止于是哉。吾与原初。皆天磨之人也。吾既以观天磨之目观枫岳而言之如此。兹者原初之往枫岳。亦以观天磨之目而观之。则其言岂有二哉。夫天下之物。有实与不实。指黔曰黔。指白曰白。固实也。若指黔曰白。指白曰黔。则岂非物之不幸哉。今吾于枫岳。正一万二千峰之讹而为数十峰。又抑天下第一之妄誇而次之于天磨。以从古昔山经地志记实之正例。庶几湔洗屡百年民人见闻话言之陋。而亦使夫枫岳者得至幸焉。顾恐梦梦之徒以吾为阿其所好。故特举枫岳僧之言以为證。原初读之。其将欣然而一笑矣。
吾不必尽数。只文笔峰,朴渊瀑。岂枫岳以下诸山之所敢望也。昔有一枫岳僧。至开城望天磨诸峰。唶曰壮矣哉。枫岳之不若也。居是邦者。其无庸游枫岳乎。彼徒从道路间见其外耳。若入其中而穷其壮富。则其说岂止于是哉。吾与原初。皆天磨之人也。吾既以观天磨之目观枫岳而言之如此。兹者原初之往枫岳。亦以观天磨之目而观之。则其言岂有二哉。夫天下之物。有实与不实。指黔曰黔。指白曰白。固实也。若指黔曰白。指白曰黔。则岂非物之不幸哉。今吾于枫岳。正一万二千峰之讹而为数十峰。又抑天下第一之妄誇而次之于天磨。以从古昔山经地志记实之正例。庶几湔洗屡百年民人见闻话言之陋。而亦使夫枫岳者得至幸焉。顾恐梦梦之徒以吾为阿其所好。故特举枫岳僧之言以为證。原初读之。其将欣然而一笑矣。大抵吾邦最大名山。为天磨枫岳。天磨处于名都大邑。而其壮雄为国中诸山之第一。枫岳处于遐陬僻澨。而其怪奇为国中诸山之第一。论枫岳如是足矣。若必欲张大其说而空天下之山。则不亦井蛙之观之蔽哉。瓜果之为物。着子多者其子小。着子少者其子大。山独不然哉。中国之地。往往置钜野平楚千馀里。大蓄气然后发泄。故其发泄于山也。多为绝大极壮之观。如庐山僧苍明(本韩京城人。俗姓朴氏。博观释书。近再访余。)所云华山三峰。于平野中。削立五千仞。全石而白。庐山瀑布。南临平野大道。其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 第 2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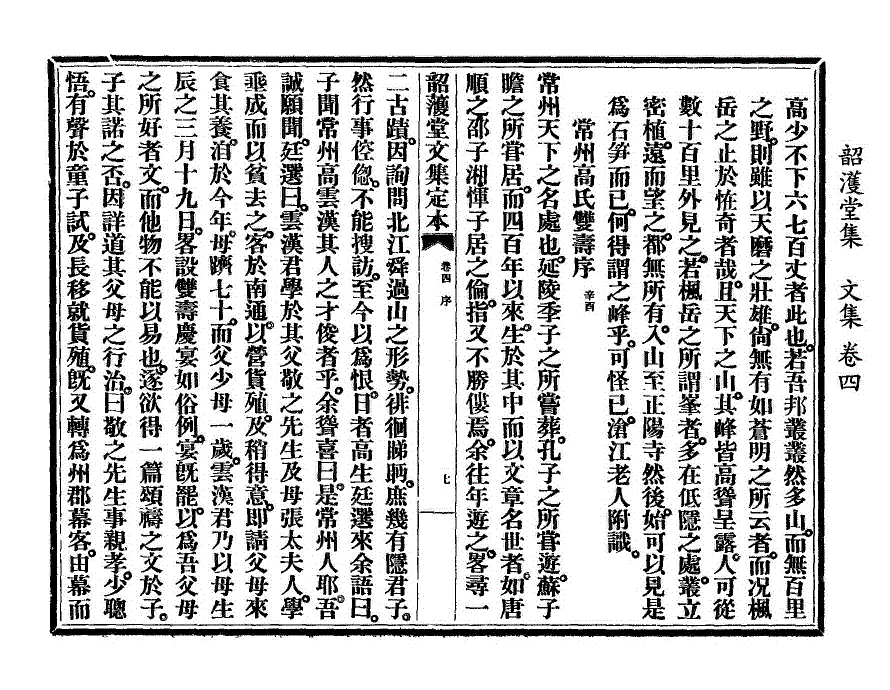 高少不下六七百丈者此也。若吾邦丛丛然多山。而无百里之野。则虽以天磨之壮雄。尚无有如苍明之所云者。而况枫岳之止于怪奇者哉。且天下之山。其峰皆高耸呈露。人可从数十百里外见之。若枫岳之所谓峰者。多在低隐之处。丛立密植。远而望之。都无所有。入山至正阳寺然后。始可以见是为石笋而已。何得谓之峰乎。可怪已。沧江老人附识。
高少不下六七百丈者此也。若吾邦丛丛然多山。而无百里之野。则虽以天磨之壮雄。尚无有如苍明之所云者。而况枫岳之止于怪奇者哉。且天下之山。其峰皆高耸呈露。人可从数十百里外见之。若枫岳之所谓峰者。多在低隐之处。丛立密植。远而望之。都无所有。入山至正阳寺然后。始可以见是为石笋而已。何得谓之峰乎。可怪已。沧江老人附识。常州高氏双寿序(辛酉)
常州天下之名处也。延陵季子之所尝葬。孔子之所尝游。苏子瞻之所尝居。而四百年以来。生于其中而以文章名世者。如唐顺之,邵子湘,恽子居之伦。指又不胜偻焉。余往年游之。略寻一二古迹。因询问北江舜过山之形势。徘徊睇眄。庶几有隐君子。然行事倥偬。不能搜访。至今以为恨。日者高生廷选来余语曰。子闻常州高云汉其人之才俊者乎。余耸喜曰。是常州人耶。吾诚愿闻。廷选曰。云汉君学于其父敬之先生及母张太夫人。学垂成而以贫去之。客于南通。以营货殖。及稍得意。即请父母来食其养。洎于今年。母跻七十。而父少母一岁。云汉君乃以母生辰之三月十九日。略设双寿庆宴如俗例。宴既罢。以为吾父母之所好者文。而他物不能以易也。遂欲得一篇颂祷之文于子。子其诺之否。因详道其父母之行治。曰敬之先生事亲孝。少聪悟。有声于童子试。及长移就货殖。既又转为州郡幕客。由幕而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 第 2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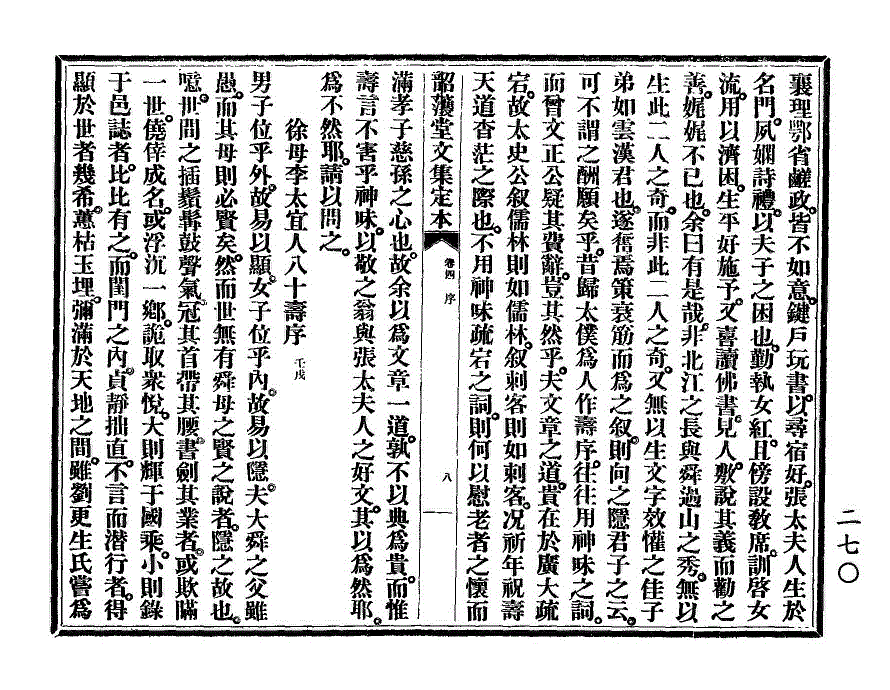 襄理鄂省鹾政。皆不如意。键户玩书。以寻宿好。张太夫人生于名门。夙娴诗礼。以夫子之困也。勤执女红。且傍设教席。训启女流。用以济困。生平好施予。又喜读佛书。见人。敷说其义而劝之善。娓娓不已也。余曰有是哉。非北江之长与舜过山之秀。无以生此二人之奇。而非此二人之奇。又无以生文字效欢之佳子弟如云汉君也。遂奋焉策衰筋而为之叙。则向之隐君子之云。可不谓之酬愿矣乎。昔归太仆为人作寿序。往往用神味之词。而曾文正公疑其费辞。岂其然乎。夫文章之道。贵在于广大疏宕。故太史公叙儒林则如儒林。叙刺客则如刺客。况祈年祝寿天道杳茫之际也。不用神味疏宕之词。则何以慰老者之怀而满孝子慈孙之心也。故余以为文章一道。孰不以典为贵。而惟寿言不害乎神味。以敬之翁与张太夫人之好文。其以为然耶。为不然耶。请以问之。
襄理鄂省鹾政。皆不如意。键户玩书。以寻宿好。张太夫人生于名门。夙娴诗礼。以夫子之困也。勤执女红。且傍设教席。训启女流。用以济困。生平好施予。又喜读佛书。见人。敷说其义而劝之善。娓娓不已也。余曰有是哉。非北江之长与舜过山之秀。无以生此二人之奇。而非此二人之奇。又无以生文字效欢之佳子弟如云汉君也。遂奋焉策衰筋而为之叙。则向之隐君子之云。可不谓之酬愿矣乎。昔归太仆为人作寿序。往往用神味之词。而曾文正公疑其费辞。岂其然乎。夫文章之道。贵在于广大疏宕。故太史公叙儒林则如儒林。叙刺客则如刺客。况祈年祝寿天道杳茫之际也。不用神味疏宕之词。则何以慰老者之怀而满孝子慈孙之心也。故余以为文章一道。孰不以典为贵。而惟寿言不害乎神味。以敬之翁与张太夫人之好文。其以为然耶。为不然耶。请以问之。徐母李太宜人八十寿序(壬戌)
男子位乎外。故易以显。女子位乎内。故易以隐。夫大舜之父虽愚。而其母则必贤矣。然而世无有舜母之贤之说者。隐之故也。噫。世间之插须髯鼓声气。冠其首带其腰。书剑其业者。或欺瞒一世。侥倖成名。或浮沉一乡。诡取众悦。大则辉于国乘。小则录于邑志者。比比有之。而闺门之内。贞静拙直。不言而潜行者。得显于世者几希。蕙枯玉埋。弥满于天地之间。虽刘更生氏尝为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 第 2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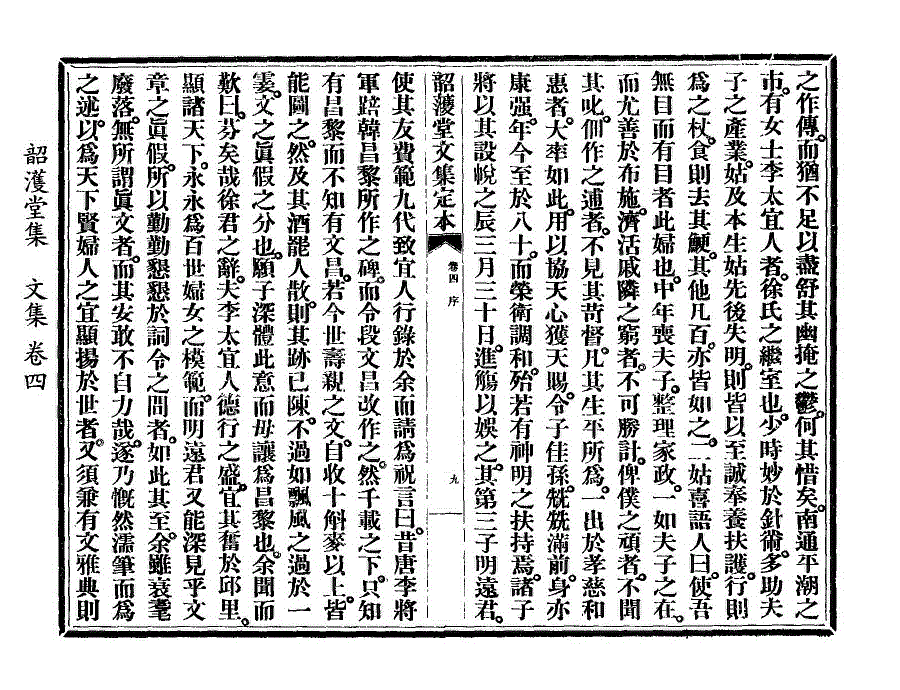 之作传。而犹不足以尽舒其幽掩之郁。何其惜矣。南通平潮之市。有女士李太宜人者。徐氏之继室也。少时妙于针黹。多助夫子之产业。姑及本生姑先后失明。则皆以至诚奉养扶护。行则为之杖。食则去其鲠。其他凡百。亦皆如之。二姑喜语人曰。使吾无目而有目者此妇也。中年丧夫子。整理家政。一如夫子之在。而尤善于布施。济活戚邻之穷者。不可胜计。俾仆之顽者。不闻其叱。佃作之逋者。不见其苛督。凡其生平所为。一出于孝慈和惠者。大率如此。用以协天心获天赐。令子佳孙。兟兟满前。身亦康强。年今至于八十。而荣卫调和。殆若有神明之扶持焉。诸子将以其设帨之辰三月三十日。进觞以娱之。其第三子明远君。使其友费范九代致宜人行录于余而请为祝言曰。昔唐李将军踣韩昌黎所作之碑。而令段文昌改作之。然千载之下。只知有昌黎而不知有文昌。若今世寿亲之文。自收十斛麦以上。皆能图之。然及其酒罢人散。则其迹已陈。不过如飘风之过于一霎。文之真假之分也。愿子深体此意而毋让为昌黎也。余闻而叹曰。芬矣哉徐君之辞。夫李太宜人德行之盛。宜其奋于邱里。显诸天下。永永为百世妇女之模范。而明远君又能深见乎文章之真假。所以勤勤恳恳于词令之间者。如此其至。余虽衰耄废落。无所谓真文者。而其安敢不自力哉。遂乃慨然濡笔而为之述。以为天下贤妇人之宜显扬于世者。又须兼有文雅典则
之作传。而犹不足以尽舒其幽掩之郁。何其惜矣。南通平潮之市。有女士李太宜人者。徐氏之继室也。少时妙于针黹。多助夫子之产业。姑及本生姑先后失明。则皆以至诚奉养扶护。行则为之杖。食则去其鲠。其他凡百。亦皆如之。二姑喜语人曰。使吾无目而有目者此妇也。中年丧夫子。整理家政。一如夫子之在。而尤善于布施。济活戚邻之穷者。不可胜计。俾仆之顽者。不闻其叱。佃作之逋者。不见其苛督。凡其生平所为。一出于孝慈和惠者。大率如此。用以协天心获天赐。令子佳孙。兟兟满前。身亦康强。年今至于八十。而荣卫调和。殆若有神明之扶持焉。诸子将以其设帨之辰三月三十日。进觞以娱之。其第三子明远君。使其友费范九代致宜人行录于余而请为祝言曰。昔唐李将军踣韩昌黎所作之碑。而令段文昌改作之。然千载之下。只知有昌黎而不知有文昌。若今世寿亲之文。自收十斛麦以上。皆能图之。然及其酒罢人散。则其迹已陈。不过如飘风之过于一霎。文之真假之分也。愿子深体此意而毋让为昌黎也。余闻而叹曰。芬矣哉徐君之辞。夫李太宜人德行之盛。宜其奋于邱里。显诸天下。永永为百世妇女之模范。而明远君又能深见乎文章之真假。所以勤勤恳恳于词令之间者。如此其至。余虽衰耄废落。无所谓真文者。而其安敢不自力哉。遂乃慨然濡笔而为之述。以为天下贤妇人之宜显扬于世者。又须兼有文雅典则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 第 271L 页
 之子如明远氏然后。其事始可以全完而无缺云尔。
之子如明远氏然后。其事始可以全完而无缺云尔。陆王二家诗钞序(壬戌)
江之北。有一奇人曰陆景骞。江之南。有一奇人曰王冰史。二人者皆以诗游于市井店铺之间。相交相爱相唱和。为乐陶陶也。一日相与拣其诗。录诸一册。问序于余。余观自古以来文章才艺之士之言议踪迹。类皆厌市井乐林水。有吸纳沆瀣清气之意想。而于吟哦之际。尤取闲静。甚至于闭门而蒙被。何其笃也。今陆君年三十馀。悔前诗之卑。变之于高古闲逸。如徐祯卿故事。王君少陆十馀岁。为诗多主工妍。取的在袁子才。若而人其锋皆可谓铦矣。然独其所处之境。非所谓吸纳沆瀣闭门蒙被者。则以至于炎炎大成也。不或难耶。此余所以惊爱其才。而旋又不胜其私悯者也。虽然余更深思之。昔韩昌黎以浮屠高闲嗜书翰。有张旭之风。为文以告曰。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而后旭可几也。将此论而深味之。则二君之求诗于市井店铺利欲之地。抑或亦一道也。于利欲熙穰纷扰之际。动心忍性。惩创激昂。有以固其精神。感而遂通。则君子之道且可至。况于诗也。何忧不能炎炎乎。二君其勉之。毋使余为空言谎说之人也哉。
姜梅山诗稿序(壬戌)
余与梅山相识者久矣。始梅山之访余汉京。不用绍介。排户径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 第 2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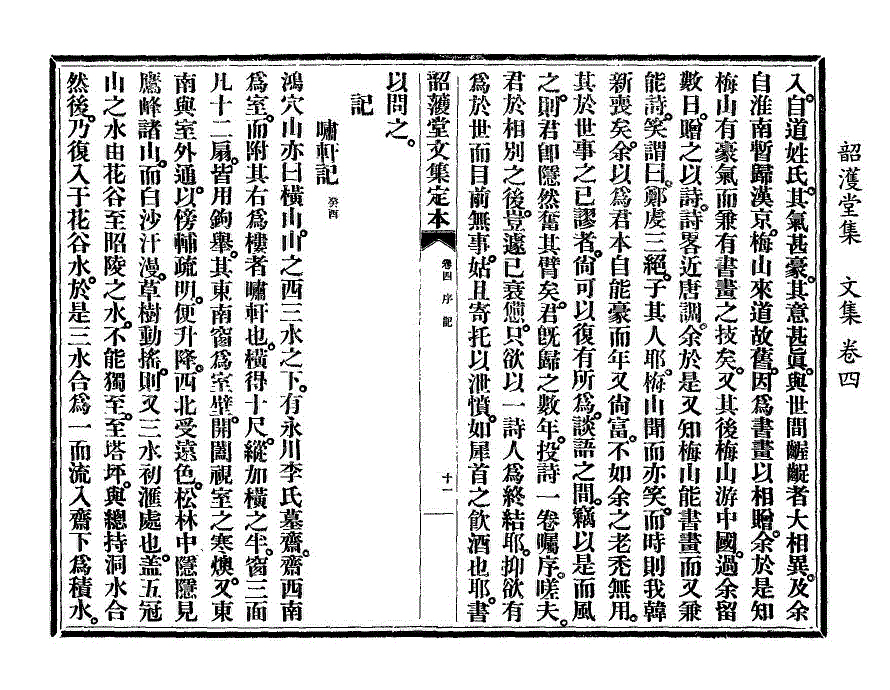 入。自道姓氏。其气甚豪。其意甚真。与世间龌龊者大相异。及余自淮南暂归汉京。梅山来道故旧。因为书画以相赠。余于是知梅山有豪气而兼有书画之技矣。又其后梅山游中国。过余留数日。赠之以诗。诗略近唐调。余于是又知梅山能书画而又兼能诗。笑谓曰。郑虔三绝。子其人耶。梅山闻而亦笑。而时则我韩新丧矣。余以为君本自能豪而年又尚富。不如余之老秃无用。其于世事之已谬者。尚可以复有所为。谈语之间。窃以是而风之。则君即隐然奋其臂矣。君既归之数年。投诗一卷嘱序。嗟夫。君于相别之后。岂遽已衰惫。只欲以一诗人为终结耶。抑欲有为于世而目前无事。姑且寄托以泄愤。如犀首之饮酒也耶。书以问之。
入。自道姓氏。其气甚豪。其意甚真。与世间龌龊者大相异。及余自淮南暂归汉京。梅山来道故旧。因为书画以相赠。余于是知梅山有豪气而兼有书画之技矣。又其后梅山游中国。过余留数日。赠之以诗。诗略近唐调。余于是又知梅山能书画而又兼能诗。笑谓曰。郑虔三绝。子其人耶。梅山闻而亦笑。而时则我韩新丧矣。余以为君本自能豪而年又尚富。不如余之老秃无用。其于世事之已谬者。尚可以复有所为。谈语之间。窃以是而风之。则君即隐然奋其臂矣。君既归之数年。投诗一卷嘱序。嗟夫。君于相别之后。岂遽已衰惫。只欲以一诗人为终结耶。抑欲有为于世而目前无事。姑且寄托以泄愤。如犀首之饮酒也耶。书以问之。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诗文集总名曰合刊韶濩堂集○花开金泽荣于霖著)
记
啸轩记(癸酉)
鸿穴山亦曰横山。山之西三水之下。有永川李氏墓斋。斋西南为室。而附其右为楼者啸轩也。横得十尺。纵加横之半。窗三面凡十二扇。皆用钩举。其东南窗为室壁。开阖视室之寒燠。又东南与室外通。以傍辅疏明。便升降。西北受远色。松林中隐隐见鹰峰诸山。而白沙汗漫。草树动摇。则又三水初汇处也。盖五冠山之水由花谷至昭陵之水。不能独至。至塔坪。与总持洞水合然后。乃复入于花谷水。于是三水合为一而流入斋下为积水。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 第 2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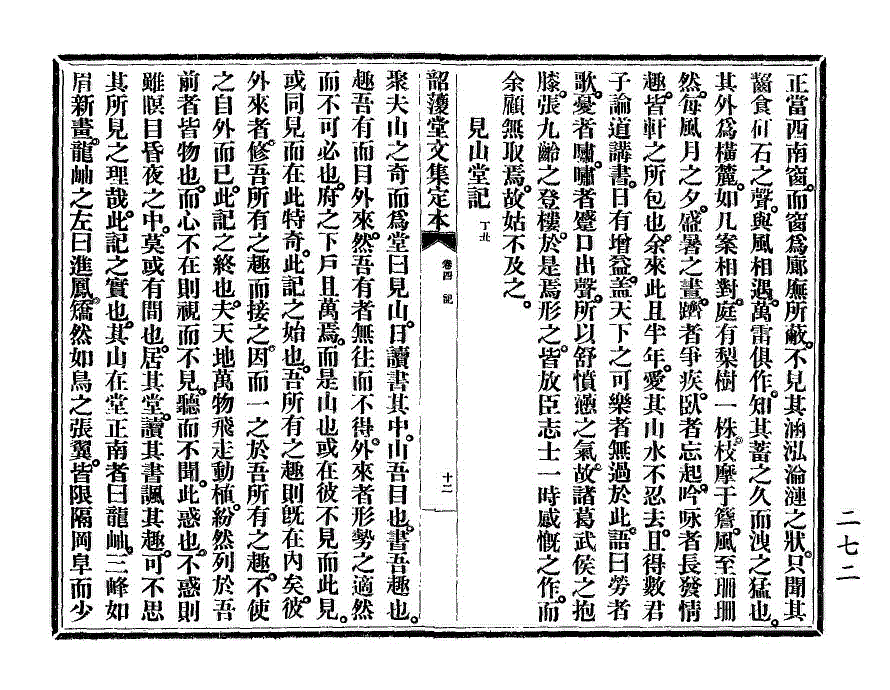 正当西南窗。而窗为廊庑所蔽。不见其涵泓沦涟之状。只闻其齧食矼石之声。与风相遇。万雷俱作。知其蓄之久而泄之猛也。其外为横麓。如几案相对。庭有梨树一株。枝摩于檐。风至珊珊然。每风月之夕。盛暑之昼。跻者争疾。卧者忘起。吟咏者长发情趣。皆轩之所包也。余来此且半年。爱其山水不忍去。且得数君子论道讲书。日有增益。盖天下之可乐者无过于此。语曰劳者歌。忧者啸。啸者蹙口出声。所以舒愤懑之气。故诸葛武侯之抱膝。张九龄之登楼。于是焉形之。皆放臣志士一时感慨之作。而余顾无取焉。故姑不及之。
正当西南窗。而窗为廊庑所蔽。不见其涵泓沦涟之状。只闻其齧食矼石之声。与风相遇。万雷俱作。知其蓄之久而泄之猛也。其外为横麓。如几案相对。庭有梨树一株。枝摩于檐。风至珊珊然。每风月之夕。盛暑之昼。跻者争疾。卧者忘起。吟咏者长发情趣。皆轩之所包也。余来此且半年。爱其山水不忍去。且得数君子论道讲书。日有增益。盖天下之可乐者无过于此。语曰劳者歌。忧者啸。啸者蹙口出声。所以舒愤懑之气。故诸葛武侯之抱膝。张九龄之登楼。于是焉形之。皆放臣志士一时感慨之作。而余顾无取焉。故姑不及之。见山堂记(丁丑)
聚夫山之奇而为堂曰见山。日读书其中。山吾目也。书吾趣也。趣吾有而目外来。然吾有者无往而不得。外来者形势之适然而不可必也。府之下户且万焉。而是山也或在彼不见而此见。或同见而在此特奇。此记之始也。吾所有之趣则既在内矣。彼外来者。修吾所有之趣而接之。因而一之于吾所有之趣。不使之自外而已。此记之终也。夫天地万物飞走动植。纷然列于吾前者皆物也。而心不在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此惑也。不惑则虽瞑目昏夜之中。莫或有间也。居其堂。读其书讽其趣。可不思其所见之理哉。此记之实也。其山在堂正南者曰龙岫。三峰如眉新画。龙岫之左曰进凤。矫然如鸟之张翼。皆限隔冈阜而少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 第 2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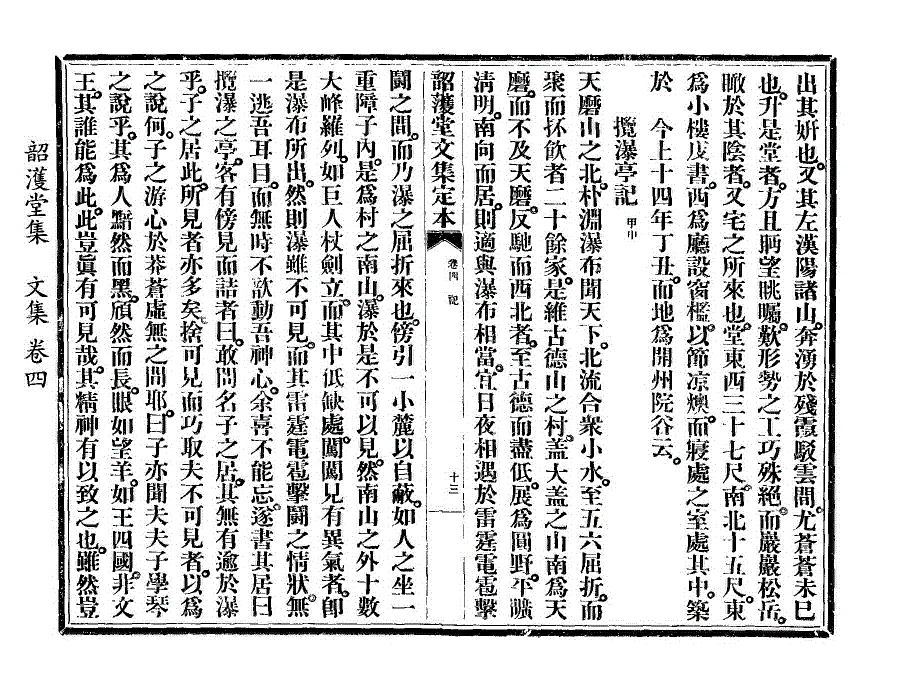 出其妍也。又其左汉阳诸山。奔涌于残霞驳云间。尤苍苍未已也。升是堂者。方且眄望眺瞩。叹形势之工巧殊绝。而岩岩松岳。瞰于其阴者。又宅之所来也。堂东西三十七尺。南北十五尺。东为小楼庋书。西为厅设窗槛。以节凉燠。而寝处之室处其中。筑于 今上十四年丁丑。而地为开州院谷云。
出其妍也。又其左汉阳诸山。奔涌于残霞驳云间。尤苍苍未已也。升是堂者。方且眄望眺瞩。叹形势之工巧殊绝。而岩岩松岳。瞰于其阴者。又宅之所来也。堂东西三十七尺。南北十五尺。东为小楼庋书。西为厅设窗槛。以节凉燠。而寝处之室处其中。筑于 今上十四年丁丑。而地为开州院谷云。揽瀑亭记(甲申)
天磨山之北。朴渊瀑布闻天下。北流合众小水。至五六屈折。而聚而抔饮者二十馀家。是维古德山之村。盖大盖之山南为天磨。而不及天磨。反驰而西北者。至古德而尽低。展为圆野。平旷清明。南向而居。则适与瀑布相当。宜日夜相遇于雷霆电雹击斗之间。而乃瀑之屈折来也。傍引一小麓以自蔽。如人之坐一重障子内。是为村之南山。瀑于是不可以见。然南山之外十数大峰罗列。如巨人杖剑立。而其中低缺处。闯闯见有异气者。即是瀑布所出。然则瀑虽不可见。而其雷霆电雹击斗之情状。无一逃吾耳目。而无时不歆动吾神心。余喜不能忘。遂书其居曰揽瀑之亭。客有傍见而诘者曰。敢问名子之居。其无有逾于瀑乎。子之居此。所见者亦多矣。舍可见而巧取夫不可见者。以为之说何。子之游心于莽苍虚无之间耶。曰子亦闻夫夫子学琴之说乎。其为人黯然而黑。颀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此岂真有可见哉。其精神有以致之也。虽然岂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 第 2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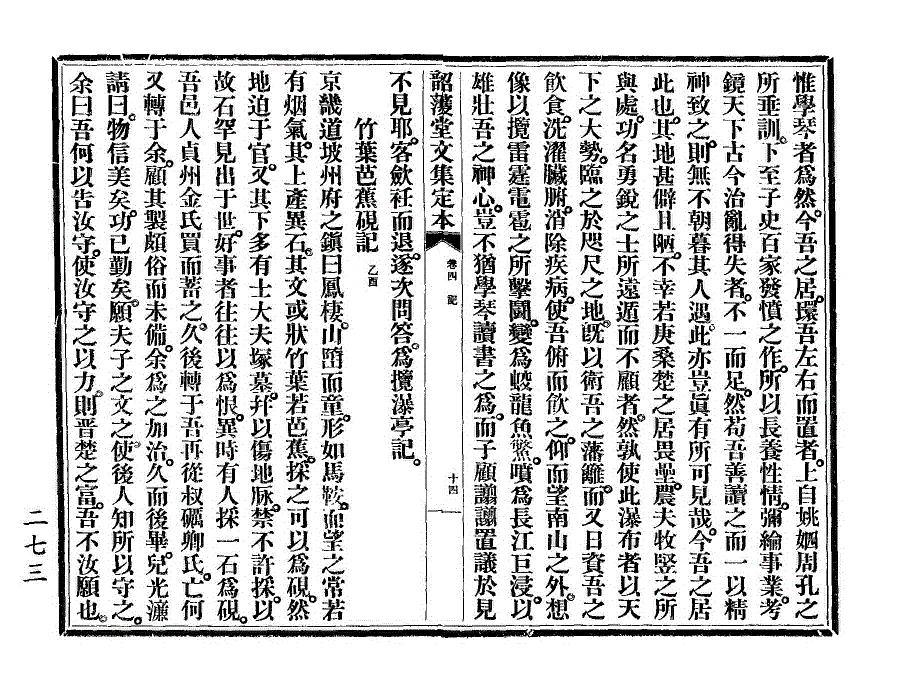 惟学琴者为然。今吾之居。环吾左右而置者。上自姚
惟学琴者为然。今吾之居。环吾左右而置者。上自姚竹叶芭蕉砚记(乙酉)
京畿道坡州府之镇曰凤栖。山嶞而童。形如马鞍。而望之常若有烟气。其上产异石。其文或状竹叶若芭蕉。采之可以为砚。然地迫于官。又其下多有士大夫冢墓。并以伤地脉。禁不许采。以故石罕见出于世。好事者往往以为恨。异时有人采一石为砚。吾邑人贞州金氏买而蓄之。久后转于吾再从叔砺卿氏。亡何又转于余。顾其制颇俗而未备。余为之加治。久而后毕。儿光濂请曰。物信美矣。功已勤矣。愿夫子之文之。使后人知所以守之。余曰吾何以告汝守。使汝守之以力。则晋楚之富。吾不汝愿也。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 第 2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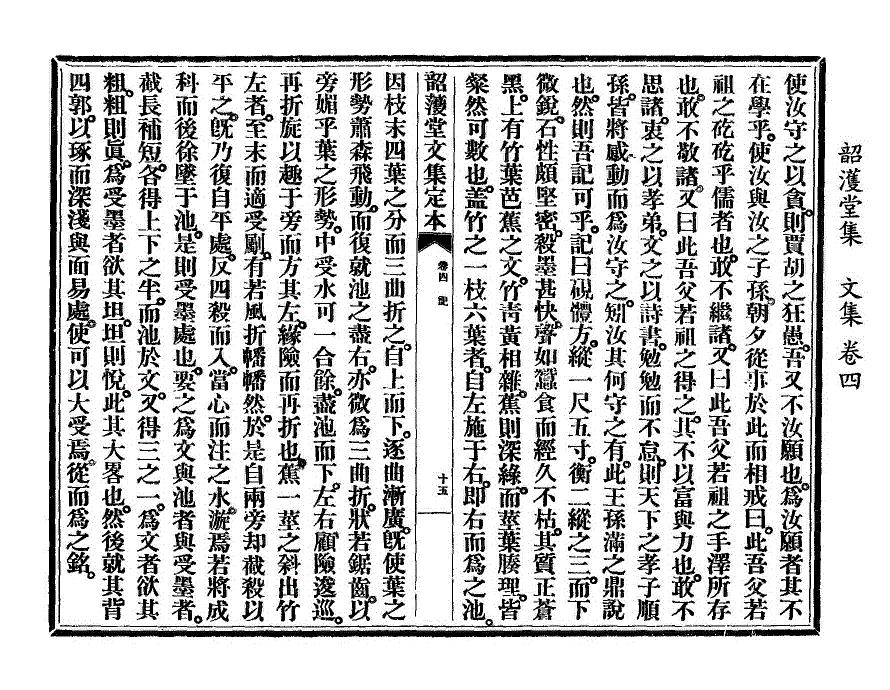 使汝守之以贪。则贾胡之狂愚。吾又不汝愿也。为汝愿者其不在学乎。使汝与汝之子孙。朝夕从事于此而相戒曰。此吾父若祖之矻矻乎儒者也。敢不继诸。又曰此吾父若祖之手泽所存也。敢不敬诸。又曰此吾父若祖之得之。其不以富与力也。敢不思诸。衷之以孝弟。文之以诗书。勉勉而不怠。则天下之孝子顺孙。皆将感动而为汝守之。矧汝其何守之有。此王孙满之鼎说也。然则吾记可乎。记曰砚体方。纵一尺五寸。衡二纵之三。而下微锐。石性颇坚密。杀墨甚快。声如蚕食而经久不枯。其质正苍黑。上有竹叶芭蕉之文。竹青黄相杂。蕉则深绿。而茎叶腠理。皆粲然可数也。盖竹之一枝六叶者。自左施于右。即右而为之池。因枝末四叶之分而三曲折之。自上而下。逐曲渐广。既使叶之形势萧森飞动。而复就池之尽右。亦微为三曲折。状若锯齿。以旁媚乎叶之形势。中受水可一合馀。尽池而下。左右顾险逡巡。再折旋以趣于旁而方其左。缘险而再折也。蕉一茎之斜出竹左者。至末而适受斸。有若风折幡幡然。于是自两旁却截杀以平之。既乃复自平处。反四杀而入。当心而注之水。漩焉若将成科而后徐坠于池。是则受墨处也。要之为文与池者与受墨者。截长补短。各得上下之半。而池于文。又得三之一。为文者欲其粗。粗则真。为受墨者欲其坦。坦则悦。此其大略也。然后就其背四郭。以琢而深浅与面易处。使可以大受焉。从而为之铭。
使汝守之以贪。则贾胡之狂愚。吾又不汝愿也。为汝愿者其不在学乎。使汝与汝之子孙。朝夕从事于此而相戒曰。此吾父若祖之矻矻乎儒者也。敢不继诸。又曰此吾父若祖之手泽所存也。敢不敬诸。又曰此吾父若祖之得之。其不以富与力也。敢不思诸。衷之以孝弟。文之以诗书。勉勉而不怠。则天下之孝子顺孙。皆将感动而为汝守之。矧汝其何守之有。此王孙满之鼎说也。然则吾记可乎。记曰砚体方。纵一尺五寸。衡二纵之三。而下微锐。石性颇坚密。杀墨甚快。声如蚕食而经久不枯。其质正苍黑。上有竹叶芭蕉之文。竹青黄相杂。蕉则深绿。而茎叶腠理。皆粲然可数也。盖竹之一枝六叶者。自左施于右。即右而为之池。因枝末四叶之分而三曲折之。自上而下。逐曲渐广。既使叶之形势萧森飞动。而复就池之尽右。亦微为三曲折。状若锯齿。以旁媚乎叶之形势。中受水可一合馀。尽池而下。左右顾险逡巡。再折旋以趣于旁而方其左。缘险而再折也。蕉一茎之斜出竹左者。至末而适受斸。有若风折幡幡然。于是自两旁却截杀以平之。既乃复自平处。反四杀而入。当心而注之水。漩焉若将成科而后徐坠于池。是则受墨处也。要之为文与池者与受墨者。截长补短。各得上下之半。而池于文。又得三之一。为文者欲其粗。粗则真。为受墨者欲其坦。坦则悦。此其大略也。然后就其背四郭。以琢而深浅与面易处。使可以大受焉。从而为之铭。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 第 2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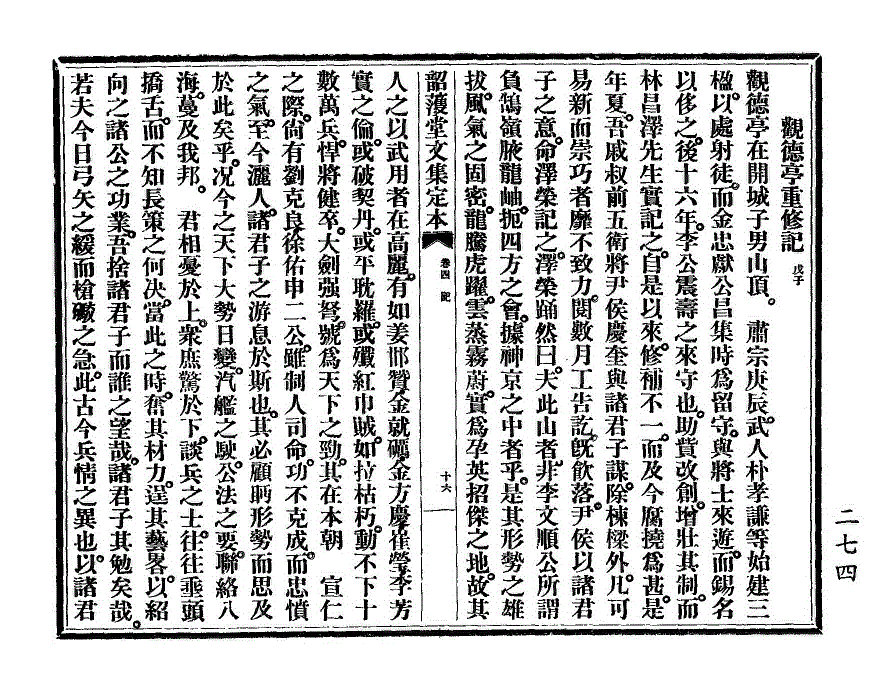 观德亭重修记(戊子)
观德亭重修记(戊子)观德亭在开城子男山顶。 肃宗庚辰。武人朴孝谦等始建三楹。以处射徒。而金忠献公昌集时为留守。与将士来游。而锡名以侈之。后十六年。李公震寿之来守也。助赀改创。增壮其制。而林昌泽先生实记之。自是以来。修补不一。而及今腐挠为甚。是年夏。吾戚叔前五卫将尹侯庆奎与诸君子谋。除栋梁外。凡可易新而崇巧者靡不致力。阅数月工告讫。既饮落。尹侯以诸君子之意。命泽荣记之。泽荣踊然曰。夫此山者。非李文顺公所谓负鹄岭腋龙岫。扼四方之会。据神京之中者乎。是其形势之雄拔。风气之固密。龙腾虎跃。云蒸雾蔚。实为孕英招杰之地。故其人之以武用者在高丽。有如姜邯赞,金就砺,金方庆,崔莹,李芳实之伦。或破契丹。或平耽罗。或歼红巾贼。如拉枯朽。动不下十数万兵。悍将健卒。大剑强弩。号为天下之劲。其在本朝 宣仁之际。尚有刘克良,徐佑申二公。虽制人司命。功不克成。而忠愤之气。至今洒人。诸君子之游息于斯也。其必顾眄形势而思及于此矣乎。况今之天下大势日变。汽舰之驶。公法之要。联络八海。蔓及我邦。 君相忧于上。众庶惊于下。谈兵之士。往往垂头挢舌。而不知长策之何决。当此之时。奋其材力。逞其艺略。以绍向之诸公之功业。吾舍诸君子而谁之望哉。诸君子其勉矣哉。若夫今日弓矢之缓而枪炮之急。此古今兵情之异也。以诸君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 第 2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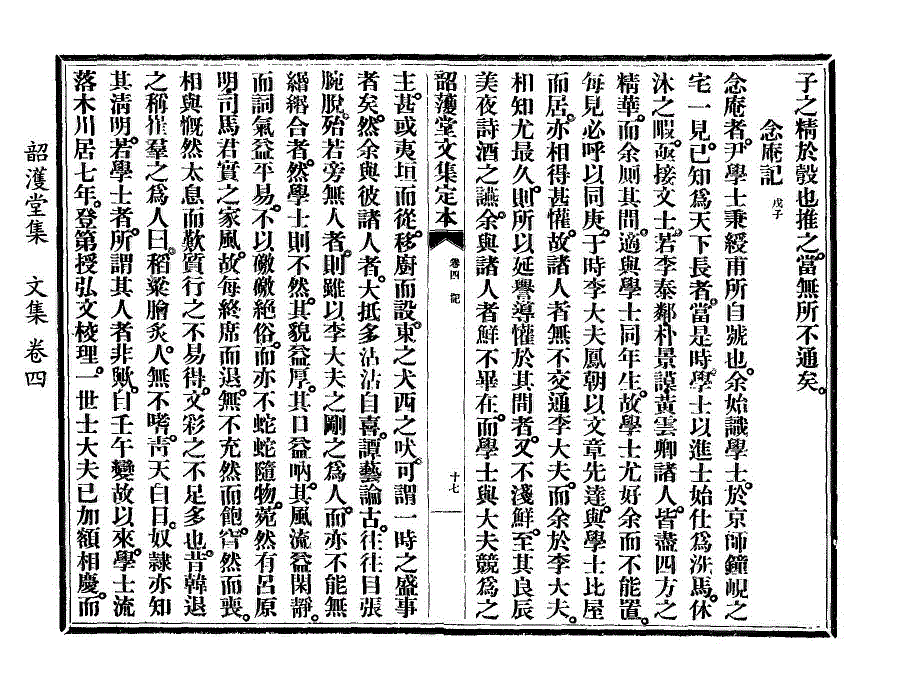 子之精于彀也推之。当无所不通矣。
子之精于彀也推之。当无所不通矣。念庵记(戊子)
念庵者。尹学士秉绶甫所自号也。余始识学士。于京师钟岘之宅一见。已知为天下长者。当是时。学士以进士始仕为洗马。休沐之暇。亟接文士。若李泰邻,朴景谟,黄云卿诸人。皆尽四方之精华。而余厕其间。适与学士同年生。故学士尤好余而不能置。每见必呼以同庚。于时李大夫凤朝以文章先达。与学士比屋而居。亦相得甚欢。故诸人者无不交通李大夫。而余于李大夫。相知尤最久。则所以延誉导欢于其间者。又不浅鲜。至其良辰美夜诗酒之宴。余与诸人者鲜不毕在。而学士与大夫竞为之主。甚或夷垣而从。移厨而设。东之犬西之吠。可谓一时之盛事者矣。然余与彼诸人者。大抵多沾沾自喜。谭艺论古。往往目张腕脱。殆若旁无人者。则虽以李大夫之刚之为人。而亦不能无缗缗合者。然学士则不然。其貌益厚。其口益呐。其风流益闲静。而词气益平易。不以礉礉绝俗。而亦不蛇蛇随物。菀然有吕原明,司马君实之家风。故每终席而退。无不充然而饱。窅然而丧。相与慨然太息而叹质行之不易得。文彩之不足多也。昔韩退之称崔群之为人曰。稻粱脍炙。人无不嗜。青天白日。奴隶亦知其清明。若学士者。所谓其人者非欤。自壬午变故以来。学士流落木川居七年。登第授弘文校理。一世士大夫已加额相庆。而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 第 2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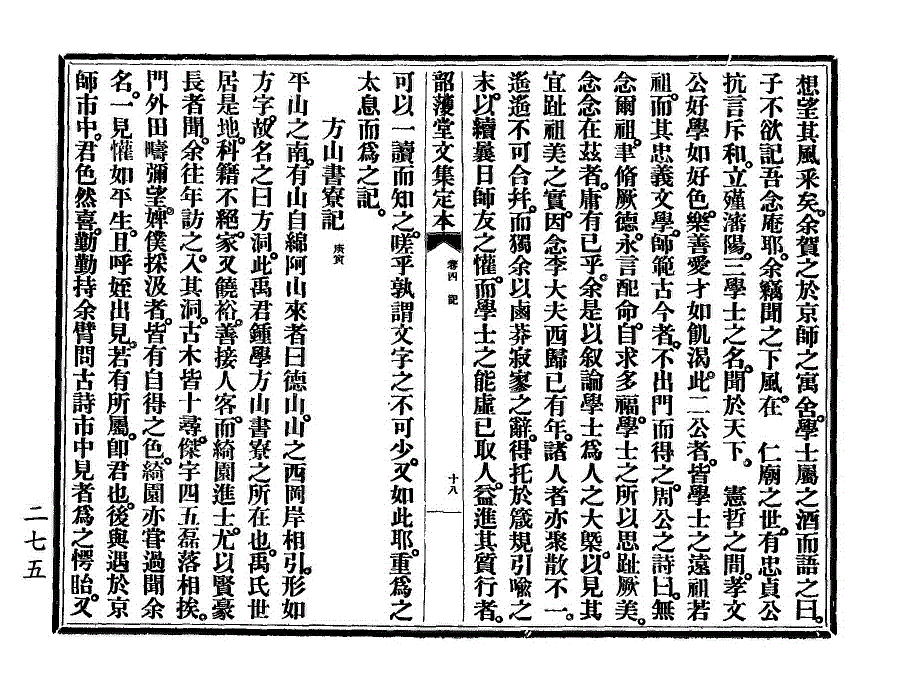 想望其风采矣。余贺之于京师之寓舍。学士属之酒而语之曰。子不欲记吾念庵耶。余窃闻之下风。在 仁庙之世。有忠贞公抗言斥和。立殣沈阳。三学士之名。闻于天下。 宪哲之间。孝文公好学如好色。乐善爱才如饥渴。此二公者。皆学士之远祖若祖。而其忠义文学。师范古今者。不出门而得之。周公之诗曰。无念尔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学士之所以思趾厥美。念念在兹者。庸有已乎。余是以叙论学士为人之大槩。以见其宜趾祖美之实。因念李大夫西归已有年。诸人者亦聚散不一。遥遥不可合并。而独余以卤莽寂寥之辞。得托于箴规引喻之末。以续曩日师友之欢。而学士之能虚己取人。益进其质行者。可以一读而知之。嗟乎孰谓文字之不可少。又如此耶。重为之太息而为之记。
想望其风采矣。余贺之于京师之寓舍。学士属之酒而语之曰。子不欲记吾念庵耶。余窃闻之下风。在 仁庙之世。有忠贞公抗言斥和。立殣沈阳。三学士之名。闻于天下。 宪哲之间。孝文公好学如好色。乐善爱才如饥渴。此二公者。皆学士之远祖若祖。而其忠义文学。师范古今者。不出门而得之。周公之诗曰。无念尔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学士之所以思趾厥美。念念在兹者。庸有已乎。余是以叙论学士为人之大槩。以见其宜趾祖美之实。因念李大夫西归已有年。诸人者亦聚散不一。遥遥不可合并。而独余以卤莽寂寥之辞。得托于箴规引喻之末。以续曩日师友之欢。而学士之能虚己取人。益进其质行者。可以一读而知之。嗟乎孰谓文字之不可少。又如此耶。重为之太息而为之记。方山书寮记(庚寅)
平山之南。有山自绵阿山来者曰德山。山之西冈岸相引。形如方字。故名之曰方洞。此禹君钟学方山书寮之所在也。禹氏世居是地。科籍不绝。家又饶裕。善接人客。而绮园进士。尤以贤豪长者闻。余往年访之。入其洞。古木皆十寻。杰宇四五磊落相挨。门外田畴弥望。婢仆采汲者。皆有自得之色。绮园亦尝过闻余名。一见欢如平生。且呼侄出见。若有所属。即君也。后与遇于京师市中。君色然喜。勤勤持余臂问古诗市中见者为之愕眙。又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 第 2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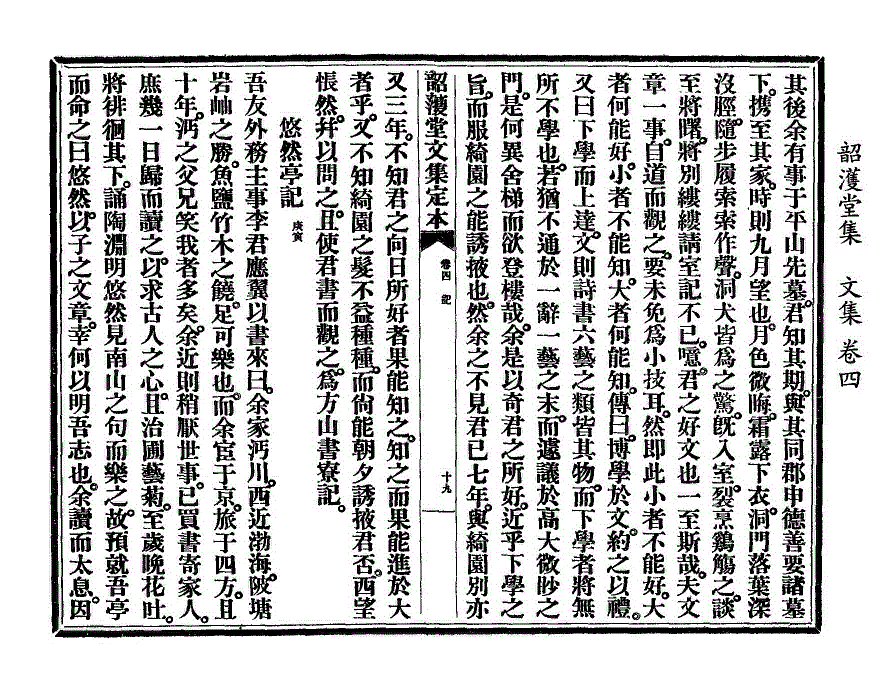 其后余有事于平山先墓。君知其期。与其同郡申德善要诸墓下。携至其家。时则九月望也。月色微晦。霜露下衣。洞门落叶深没胫。随步履索索作声。洞犬皆为之惊。既入室。裂烹鸡觞之。谈至将曙。将别缕缕请室记不已。噫。君之好文也一至斯哉。夫文章一事。自道而观之。要未免为小技耳。然即此小者不能好。大者何能好。小者不能知。大者何能知。传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又曰下学而上达。文则诗书六艺之类皆其物。而下学者将无所不学也。若犹不通于一辞一艺之末。而遽议于高大微眇之门。是何异舍梯而欲登楼哉。余是以奇君之所好。近乎下学之旨。而服绮园之能诱掖也。然余之不见君已七年。与绮园别亦又三年。不知君之向日所好者果能知之。知之而果能进于大者乎。又不知绮园之发不益种种。而尚能朝夕诱掖君否。西望怅然。并以问之。且使君书而观之。为方山书寮记。
其后余有事于平山先墓。君知其期。与其同郡申德善要诸墓下。携至其家。时则九月望也。月色微晦。霜露下衣。洞门落叶深没胫。随步履索索作声。洞犬皆为之惊。既入室。裂烹鸡觞之。谈至将曙。将别缕缕请室记不已。噫。君之好文也一至斯哉。夫文章一事。自道而观之。要未免为小技耳。然即此小者不能好。大者何能好。小者不能知。大者何能知。传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又曰下学而上达。文则诗书六艺之类皆其物。而下学者将无所不学也。若犹不通于一辞一艺之末。而遽议于高大微眇之门。是何异舍梯而欲登楼哉。余是以奇君之所好。近乎下学之旨。而服绮园之能诱掖也。然余之不见君已七年。与绮园别亦又三年。不知君之向日所好者果能知之。知之而果能进于大者乎。又不知绮园之发不益种种。而尚能朝夕诱掖君否。西望怅然。并以问之。且使君书而观之。为方山书寮记。悠然亭记(庚寅)
吾友外务主事李君应翼以书来曰。余家沔川。西近渤海。陂塘岩岫之胜。鱼盐竹木之饶。足可乐也。而余宦于京。旅于四方。且十年。沔之父兄笑我者多矣。余近则稍厌世事。已买书寄家人。庶几一日归而读之。以求古人之心。且治圃艺菊。至岁晚花吐。将徘徊其下。诵陶渊明悠然见南山之句而乐之。故预就吾亭而命之曰悠然。以子之文章。幸何以明吾志也。余读而太息。因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 第 2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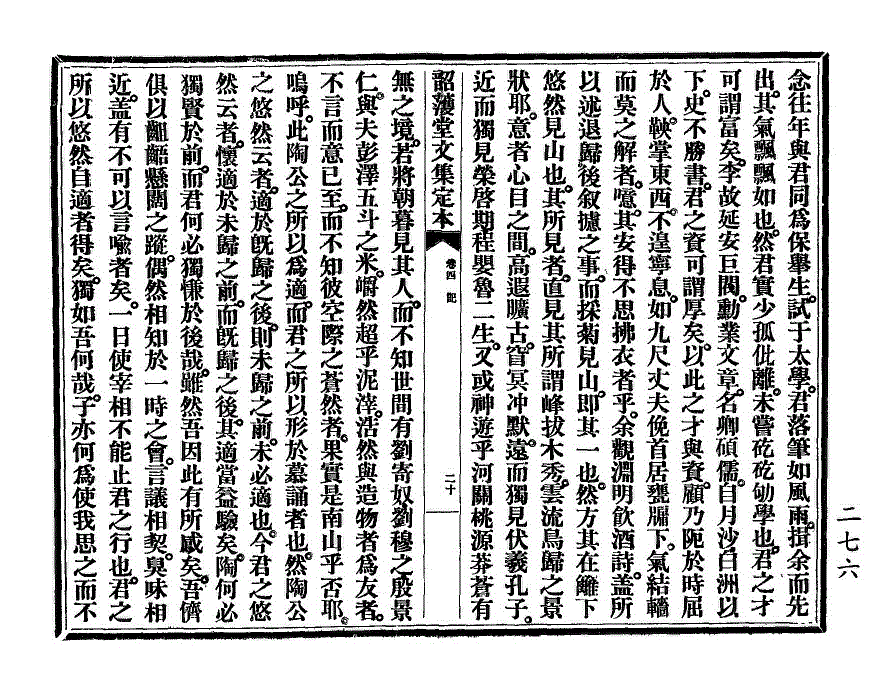 念往年与君同为保举生。试于太学。君落笔如风雨。揖余而先出。其气飘飘如也。然君实少孤仳离。未尝矻矻劬学也。君之才可谓富矣。李故延安巨阀。勋业文章。名卿硕儒。自月沙,白洲以下。史不胜书。君之资可谓厚矣。以此之才与资。顾乃阨于时屈于人。鞅掌东西。不遑宁息。如九尺丈夫俛首居瓮牖下。气结轖而莫之解者。噫。其安得不思拂衣者乎。余观渊明饮酒诗。盖所以述退归后叙摅之事。而采菊见山。即其一也。然方其在篱下悠然见山也。其所见者。直见其所谓峰拔木秀。云流鸟归之景状耶。意者心目之间。高遐旷古。窅冥冲默。远而独见伏羲孔子。近而独见荣启期,程婴鲁二生。又或神游乎河关桃源莽苍有无之境。若将朝暮见其人。而不知世间有刘寄奴,刘穆之,殷景仁。与夫彭泽五斗之米。皭然超乎泥滓。浩然与造物者为友者。不言而意已至。而不知彼空际之苍然者。果实是南山乎否耶。呜呼。此陶公之所以为适。而君之所以形于慕诵者也。然陶公之悠然云者。适于既归之后。则未归之前。未必适也。今君之悠然云者。怀适于未归之前。而既归之后。其适当益验矣。陶何必独贤于前。而君何必独慊于后哉。虽然吾因此有所感矣。吾侪俱以龃龉悬阔之踪。偶然相知于一时之会。言议相契。臭味相近。盖有不可以言喻者矣。一日使宰相不能止君之行也。君之所以悠然自适者得矣。独如吾何哉。子亦何为使我思之而不
念往年与君同为保举生。试于太学。君落笔如风雨。揖余而先出。其气飘飘如也。然君实少孤仳离。未尝矻矻劬学也。君之才可谓富矣。李故延安巨阀。勋业文章。名卿硕儒。自月沙,白洲以下。史不胜书。君之资可谓厚矣。以此之才与资。顾乃阨于时屈于人。鞅掌东西。不遑宁息。如九尺丈夫俛首居瓮牖下。气结轖而莫之解者。噫。其安得不思拂衣者乎。余观渊明饮酒诗。盖所以述退归后叙摅之事。而采菊见山。即其一也。然方其在篱下悠然见山也。其所见者。直见其所谓峰拔木秀。云流鸟归之景状耶。意者心目之间。高遐旷古。窅冥冲默。远而独见伏羲孔子。近而独见荣启期,程婴鲁二生。又或神游乎河关桃源莽苍有无之境。若将朝暮见其人。而不知世间有刘寄奴,刘穆之,殷景仁。与夫彭泽五斗之米。皭然超乎泥滓。浩然与造物者为友者。不言而意已至。而不知彼空际之苍然者。果实是南山乎否耶。呜呼。此陶公之所以为适。而君之所以形于慕诵者也。然陶公之悠然云者。适于既归之后。则未归之前。未必适也。今君之悠然云者。怀适于未归之前。而既归之后。其适当益验矣。陶何必独贤于前。而君何必独慊于后哉。虽然吾因此有所感矣。吾侪俱以龃龉悬阔之踪。偶然相知于一时之会。言议相契。臭味相近。盖有不可以言喻者矣。一日使宰相不能止君之行也。君之所以悠然自适者得矣。独如吾何哉。子亦何为使我思之而不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 第 277H 页
 得见。登高而望。湖海之间。群山出没。云霞飞涌其中。辄怅然举手语曰彼或悠然亭之南山也耶。
得见。登高而望。湖海之间。群山出没。云霞飞涌其中。辄怅然举手语曰彼或悠然亭之南山也耶。鹳归轩记(辛卯)
开城府南二十里小墨池里。有大地洞。盖古时有葬师过而指之曰此大地也故名。而俗或以地为池。不知何为。近又转讹曰智异洞。洞之北山。有我六世祖以下三世之葬。而山水气势绝胜。人之游观乎此者。自下而仰之。若凤之羾于天。自上而頫之。若龙之降于渊。得于昭明者。无不足于幽密。得于雄杰者。无不足于稳藉。莫不知其为精气之所融聚。造物者之所安排者。术家所论阴阳灾荫。其说甚多。然吾不能知其如何。而独尝闻夫贤人之所在。必有青云德星之覆照。荆棘蓬蒿不入于昌平之闾。以吾先祖仁义孝友之德。虽不见知于当世之人。终于幽闇。而天地山川之神则明知之久矣。岂肯使其肤骨亲于朽壤浊泉而已也。呜呼。先祖其尚安乐乎哉。墓之下。旧有丙舍一座。为我从高祖赠左承旨讳宗禄公之所建。而制极坚致。垂及百年。无有欹患。(六代五代墓石仪。亦为承旨公所具。)是秋泽荣奉父兄命。领工来设游窗之属。因留读书。得朝夕昵侍乎英灵之侧。既用怆感而旋以忻乐。何则。因先祖之安乐也。先墓右角大杉树上。有鹳来巢者近十年。去年官使捕鹳。捕者潜伺三日夜。竟不见鹳而去。守墓者以为神。一日余上墓。适有鹳一群。自西南来集于杉。守墓者向余言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 第 2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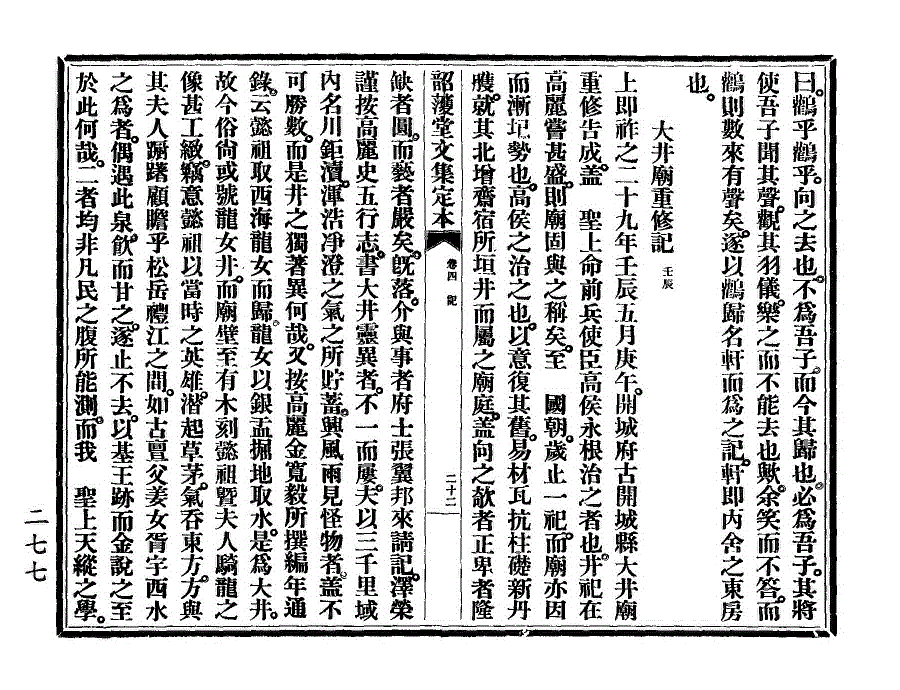 曰。鹳乎鹳乎。向之去也。不为吾子。而今其归也。必为吾子。其将使吾子闻其声。观其羽仪。乐之而不能去也欤。余笑而不答。而鹳则数来有声矣。遂以鹳归名轩而为之记。轩即丙舍之东房也。
曰。鹳乎鹳乎。向之去也。不为吾子。而今其归也。必为吾子。其将使吾子闻其声。观其羽仪。乐之而不能去也欤。余笑而不答。而鹳则数来有声矣。遂以鹳归名轩而为之记。轩即丙舍之东房也。大井庙重修记(壬辰)
上即祚之二十九年壬辰五月庚午。开城府古开城县大井庙重修告成。盖 圣上命前兵使臣高侯永根治之者也。井祀在高丽尝甚盛。则庙固与之称矣。至 国朝。岁止一祀。而庙亦因而渐圮势也。高侯之治之也。以意复其旧。易材瓦抗柱础新丹雘。就其北增斋宿所垣井而属之庙庭。盖向之欹者正卑者隆缺者圆。而亵者严矣。既落。介与事者府士张翼邦来请记。泽荣谨按高丽史五行志。书大井灵异者。不一而屡。夫以三千里域内名川钜渎。浑浩净澄之气之所贮蓄。兴风雨见怪物者。盖不可胜数。而是井之独著异何哉。又按高丽金宽毅所撰编年通录。云懿祖取西海龙女而归。龙女以银盂掘地取水。是为大井。故今俗尚或号龙女井。而庙壁至有木刻懿祖暨夫人骑龙之像甚工致。窃意懿祖以当时之英雄。潜起草茅。气吞东方。方与其夫人蹰躇顾瞻乎松岳礼江之间。如古亶父姜女胥宇西水之为者。偶遇此泉。饮而甘之。遂止不去。以基王迹而金说之至于此何哉。二者均非凡民之腹所能测。而我 圣上天纵之学。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 第 2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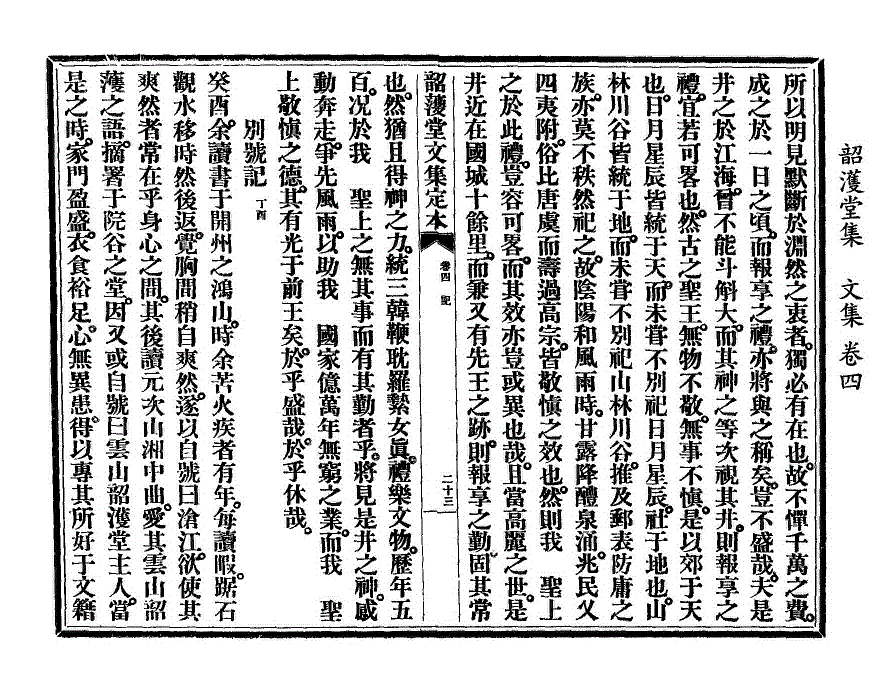 所以明见默断于渊然之衷者。独必有在也。故不惮千万之费。成之于一日之顷。而报享之礼。亦将与之称矣。岂不盛哉。夫是井之于江海。曾不能斗斛大。而其神之等次视其井。则报享之礼。宜若可略也。然古之圣王。无物不敬。无事不慎。是以郊于天也。日月星辰皆统于天。而未尝不别祀日月星辰。社于地也。山林川谷皆统于地。而未尝不别祀山林川谷。推及邮表防庸之族。亦莫不秩然祀之。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醴泉涌。兆民乂四夷附。俗比唐虞而寿过高宗。皆敬慎之效也。然则我 圣上之于此礼。岂容可略。而其效亦岂或异也哉。且当高丽之世。是井近在国城十馀里。而兼又有先王之迹。则报享之勤。固其常也。然犹且得神之力。统三韩鞭耽罗絷女真。礼乐文物。历年五百。况于我 圣上之无其事而有其勤者乎。将见是井之神。感动奔走。争先风雨。以助我 国家亿万年无穷之业。而我 圣上敬慎之德。其有光于前王矣。于乎盛哉。于乎休哉。
所以明见默断于渊然之衷者。独必有在也。故不惮千万之费。成之于一日之顷。而报享之礼。亦将与之称矣。岂不盛哉。夫是井之于江海。曾不能斗斛大。而其神之等次视其井。则报享之礼。宜若可略也。然古之圣王。无物不敬。无事不慎。是以郊于天也。日月星辰皆统于天。而未尝不别祀日月星辰。社于地也。山林川谷皆统于地。而未尝不别祀山林川谷。推及邮表防庸之族。亦莫不秩然祀之。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醴泉涌。兆民乂四夷附。俗比唐虞而寿过高宗。皆敬慎之效也。然则我 圣上之于此礼。岂容可略。而其效亦岂或异也哉。且当高丽之世。是井近在国城十馀里。而兼又有先王之迹。则报享之勤。固其常也。然犹且得神之力。统三韩鞭耽罗絷女真。礼乐文物。历年五百。况于我 圣上之无其事而有其勤者乎。将见是井之神。感动奔走。争先风雨。以助我 国家亿万年无穷之业。而我 圣上敬慎之德。其有光于前王矣。于乎盛哉。于乎休哉。别号记(丁酉)
癸酉。余读书于开州之鸿山。时余苦火疾者有年。每读暇。踞石观水移时然后返。觉胸间稍自爽然。遂以自号曰沧江。欲使其爽然者常在乎身心之间。其后读元次山湘中曲。爱其云山韶濩之语。摘署于院谷之堂。因又或自号曰云山韶濩堂主人。当是之时。家门盈盛。衣食裕足。心无异患。得以专其所好于文籍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 第 2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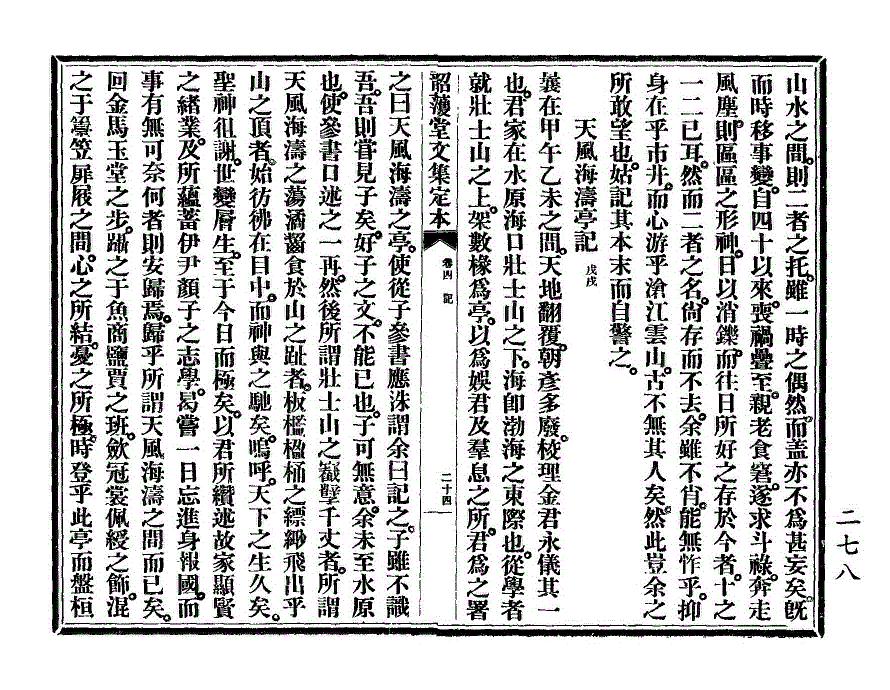 山水之间。则二者之托。虽一时之偶然。而盖亦不为甚妄矣。既而时移事变。自四十以来。丧祸叠至。亲老食窘。遂求斗禄。奔走风尘。则区区之形神。日以消铄。而往日所好之存于今者。十之一二已耳。然而二者之名。尚存而不去。余虽不肖。能无怍乎。抑身在乎市井。而心游乎沧江云山。古不无其人矣。然此岂余之所敢望也。姑记其本末而自警之。
山水之间。则二者之托。虽一时之偶然。而盖亦不为甚妄矣。既而时移事变。自四十以来。丧祸叠至。亲老食窘。遂求斗禄。奔走风尘。则区区之形神。日以消铄。而往日所好之存于今者。十之一二已耳。然而二者之名。尚存而不去。余虽不肖。能无怍乎。抑身在乎市井。而心游乎沧江云山。古不无其人矣。然此岂余之所敢望也。姑记其本末而自警之。天风海涛亭记(戊戌)
曩在甲午乙未之间。天地翻覆。朝彦多废。校理金君永仪其一也。君家在水原海口壮士山之下。海即渤海之东际也。从学者就壮士山之上。架数椽为亭。以为娱君及群息之所。君为之署之曰天风海涛之亭。使从子参书应洙谓余曰记之。子虽不识吾。吾则尝见子矣。好子之文。不能已也。子可无意。余未至水原也。使参书口述之一再。然后所谓壮士山之巀孽千丈者。所谓天风海涛之荡潏齧食于山之趾者。板槛楹桷之缥缈飞出乎山之顶者。始彷佛在目中。而神与之驰矣。呜呼。天下之生久矣。圣神徂谢。世变层生。至于今日而极矣。以君所缵述故家显贤之绪业。及所蕴蓄伊尹颜子之志学。曷尝一日忘进身报国。而事有无可奈何者则安归焉。归乎所谓天风海涛之间而已矣。回金马玉堂之步。蹑之于鱼商盐贾之班。敛冠裳佩绶之饰。混之于籉笠屝屐之间。心之所结。忧之所极。时登乎此亭而盘桓
韶濩堂文集定本卷四 第 279H 页
 焉。则彼其天海渺茫。何翅数千万里。岛屿之沉浸。舟楫之容与。蛟龙鱼鳖之出没。凫雁鹅鸭之飞止。日月云烟之明鲜绚烂。景状万千。左右纷集。有可以使人悠然而忘忧者矣。君其舍此而何之哉。然吾试想像。日之将夕。天风益发。海波益荡。苍茫倏忽。远近有无之际。孰为击磬襄之所从入者乎。孰为孔子之所欲桴者乎。孰为鲁仲连先生之所欲蹈者乎。吾又恐君之忧有时乎复作而不能以久留也。
焉。则彼其天海渺茫。何翅数千万里。岛屿之沉浸。舟楫之容与。蛟龙鱼鳖之出没。凫雁鹅鸭之飞止。日月云烟之明鲜绚烂。景状万千。左右纷集。有可以使人悠然而忘忧者矣。君其舍此而何之哉。然吾试想像。日之将夕。天风益发。海波益荡。苍茫倏忽。远近有无之际。孰为击磬襄之所从入者乎。孰为孔子之所欲桴者乎。孰为鲁仲连先生之所欲蹈者乎。吾又恐君之忧有时乎复作而不能以久留也。